弁言
三民主义
唐六典
通典
建国方略
政学私言
孔子与中国之道
简介
中文版书名: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英文名: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
作者:【美】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
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年1月19日-1994年6月1日),生于芝加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曾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亚洲学会会员等,是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同时也是孔子研究的权威。曾著有《孔子与中国之道》、《孔子真面目》、《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传说中之孔子》多书。
顾立雅的孔子观对现代的欧美人士影响颇大。他的著作,特别是《孔子与中国之道》,一向是西方汉学界孔子研究领域学者的必备参考书。他对中国初期汉学的贡献亦使芝加哥大学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
译者:高专诚
出版社:郑州:大象出版社
ISBN 978-7-5347-7962-6
本书概要
瘟疫刚爆发时标记过。作者受顾颉刚之流影响比较大,荒唐言较多。不过关于欧美、中华民国和儒学的关系的考证极具启发性,虽然是神州陆沉前的作品,还是远超今日上窜下跳的货色的作品!
这本书最大的缺点就是受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和以胡适之流的乡愿影响太大,以至于关于尧舜禹孔子的一切都被否定了。而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就是论证了孔子思想和自由共和思想拟合性,而且用丰富的史料证明了孔子对欧美特别是法国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形成的巨大影响,而且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欧洲的孔夫子魁奈对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直接影响(laissez-faire即自由放任来源于无为),从整体上看应该是中华文明而不是基督教文明和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一起构建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而历史经验表明基督教和它的两个衍生教即伊斯兰教和马列教给全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而且这种灾难还将持续很多年!!
爱默生(Emerson)是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美国总统林肯称他为”美国的孔夫子“、”美国文明之父“,以爱默生思想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是美国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被称为”美国文艺复兴“。
维基百科上爱默生条目下这段话来源不定,本人搜索只发现爱思想网上有文章(《刘悦笛:美国超验主义与儒家世界观——孔孟与爱默生的深层对话与介入重构》)提到这点,英文的内容也有但是不是正规出版物,而且基本和Chinese相关。网上的英文文本内容如下:
Emerson is an iconic figure inAmerican culture, and PresidentAbraham Lincoln called him"America's Confucius" and "thefather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Transcendentalism, represented byEmerson's ideas, was an importantintellectual liberation movement inthe history of American thought andhas been called the "AmericanRenaissance.
搜索到的唯一出版物是GoogleBook上的如下这本书:
| 名称 | Emerson, the American Confucius: An Exploration of Confucian Motifs in the Early Writings (1830-1843) of Ralph Waldo Emerson |
| 作者 | Kyle Bryant Simmons |
| 撰稿人 |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Graduate Program in the Humanities |
| 出版商 |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2013 |
| 页数 | 718页 |
但是就这本书的简介来看,没有提到林肯。这个暂且保留,以后再说。
Henry David Thoreau在其在代表作《瓦尔登湖》中多次引用来自《论语》等书中的话。
此外孔子出现在美国最高法院的雕像中也是儒学对美国产生的影响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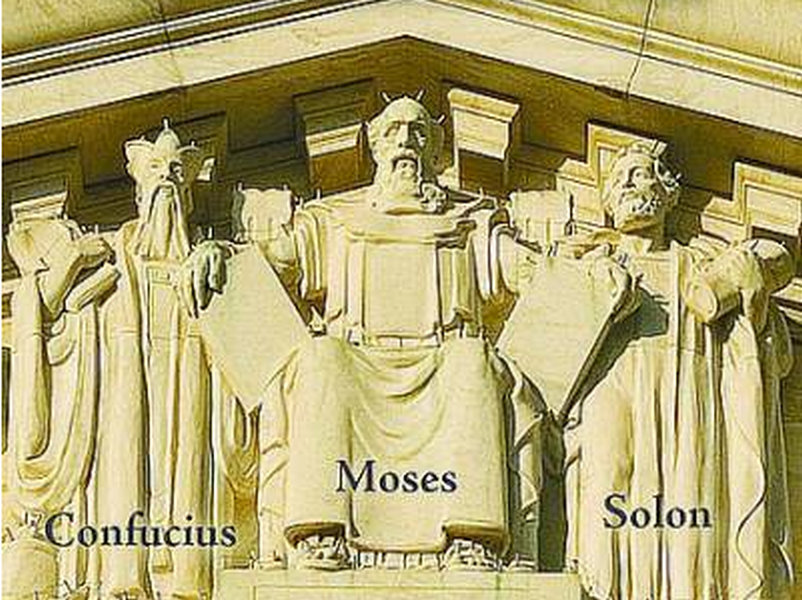
Confucius, Moses, and Salon in the east gate of the Federal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原则上来说,不能拿洋人的点赞当门面,但是洋奴除了洋人的话根本什么都听不进去,洋大人认证的东西放在它们面前才能让它们少吠几句!
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第一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
本书译者下了很大功夫,在注释中对顾立雅很多错误的说法进行了批驳和改正。这个给个👍!
不过译文也有较多错误,比如p6沃尔夫的生年是1679不是1629、p275杜霍尔德(Du Halde)生卒年应该是1674—1743。
虽然本书作者是美国人,但是本书主要讲述孔子,故放在中文书籍栏目中。
孔子与中国之道全文
总序一
作者:任继愈
总序二
作者:张西平
同时也应看到,海外中国学与中国近现代的中国学术进展紧密相连。从晚明时开始,在全球化的初期,中国已经被卷入世界的贸易体系之中,关于中国的知识、文化、历史、典籍已经开始被这些来华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研究。从那时起,中国的知识已经不完全归中国学者独有,开始有了另一套讲述中国文化和学术的新的叙述,这就是海外中国文化研究(汉学或中国学)。而且在1814年的法国,他们已经把中国研究列入其正式的教育系统之中,在西方东方学中开始有了一门新学问——汉学。
新版译序
时光荏苒,距离上一次审改译文,又是10年的光阴。这本书从20年前在山西人民出版社付梓,到10年前在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20年间被许多读者视为良友,也一直是我的枕边书。何其幸也!这是一部好书,当然主要原因是原作者写得好,但是译者的全身心投入,也应该是原因之一吧。
20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并随之开始以翻译的方式加深阅读,其结构之合理、分析之深入、材料之广博、行文之严谨,深刻影响了我的学术生涯。如今再次重译,忽然意识到,原著者对孔子和孔子弟子是倾注了很深的感情的,而这样的感情也是做传统学问所必需的。受原著者感情投入的影响,此次重译,断断续续进行了两年,力图使全书的面貌有所改观,也使自己再次受益,再次有所进步。
此译本自20多年前出版以来,经过了多次重印和小的修修补补,一直深受学界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我自己也经常阅读,自然会经常发现一些小的舛误,更意识到还有一些缺陷是非补不可的。2011年,与大象出版社商议之后,决定作一次较大的修改和增补,主要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修改译文方面的失检和失误,在自查之际,亦参考了王正义之译本(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在此特别表示感谢。二是根据这些年来研习孔子及孔子弟子生平及思想之所得,增加了一些“译按”,力图对顾氏原著的一些观点予以商榷和再商榷。三是对许多引文的出处,特别是古文的出处,作了必要的增补,以期最大程度地方便读者的阅读和参考。
此次重译虽多沥心血,然而正所谓“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不妥或失当之处势必仍有,故非常期盼方家和读者的指正。
付梓之际,特向大象出版社及本书责编李光洁女士致以深切感谢,感谢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辛勤付出。
高专诚
2012年11月22日
英文版作者自序
在很多人类群体中,都把孔子看作是许多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历史人物。在现代西方的某些最基本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孔子思想发挥过作用。在东亚,孔子的名字仍然引发着一些思想最保守者与最激进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他们都在寻求对于有关资料的种种不同注释的蕴意,以证明孔子赞同他们的观点。
当我们从孔子在其身后的历史上所获得的荣耀着手去审视那种告诉我们这位历史人物在世时之情形的传统说法时,我们失望了。在这些传统说法中,孔子被说得毫无独创性,仅仅是热衷于复兴古代的习俗。在对他的生平事迹的叙述中,孔子在总体上被描述成一个没有个人魄力的人,他的行为也经常与他讲述给他人的思想背道而驰。这种情况不能不让人认为,肯定有某种东西出了差错。传统说法所描绘的这个人与历史事实所显示的情形不甚相当。对此,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传统说法并没有实事求是地描述曾经在人世间生活过的孔子。本书就是对这种可能性的探究。
本书所作的这种探究当然不是寻找真孔子的首次尝试,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如果本书的努力能被证明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的话,作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
书中仍有的任何差错均由我一人负责。因为它的主题是庞大而复杂的,无疑会有许多错误。对此,我的态度正如《论语·宪问十四》中提到的一个人所说的:“本想使过错减少一些,但却还没有完全实现(欲寡其过而未能也)。”
背景
第一章 传统说法与实情
2500年前,中国降生了一个婴孩,他的一生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提并论。传统说法认为,他是贵族之后,还是帝王的后裔。 [1] 他临世之时,据说有苍龙和“神女”在空中盘旋。 [2] 但是,孔子自己却说:“年轻时我没有社会地位,还生活在卑贱的环境中。” [3]
【按:海昏侯墓屏风中有”野居而生“的话,把《史记》所记载的”野合而生“视为传抄错误是最合理的解释。】
传统说法把孔子看成一位严厉的学究,说他制定下细致的规则让人们言行是比。实情却是,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制定死板的规则,因为他坚信,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遵循他人制定好的教条,更不可能因此就免去反躬自思的义务。
【按:因材施教的孔子一以贯之的是道,或者说是原则, 具体的要求或建议都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的。】
在政治上,孔子通常被认为是保守分子,甚至还有人说他的首要目标是复古和捍卫世袭贵族的政治特权。事实上,孔子倡导和促进了一场彻底的社会和政治革新,所以,他应被看作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变革者。在他去世后的几个世纪之内,盛行于他那个时代的世卿世禄的政治制度最终在中国消亡了。对于这一旧制度的崩溃,孔子的贡献大于任何人。
【按:孔子开私学,向已经沦为平民的贵族子弟提供周礼规定的教育,使他们成为具有担当精神的士,为中国文明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新鲜的血液——贤人,从而使得礼崩乐坏、仁义充塞之后仍有忠义之士在黑暗中传递文明的火种,从这个角度来看,”天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是非常合理的评价!】
年轻时的孔子不得不自己谋生,以至于去做一些卑贱之事。 [4] 从这些经历中,孔子得到并且从未失去的是对普通人的深切同情。他们遇到了太多的难题,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周朝的中央集权政府已经瓦解,封建诸侯只是名义上臣服于周天子。然而,这些诸侯并不能说是独立的,因为其中的一些又成为他们的家臣的傀儡。在诸侯国和各国贵族之间,公开的和私下的争斗愈演愈烈。各国诸侯根本无力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规,以使他们避免受制于自己的得力助手、拥有武装的属下或者竭力僭夺他们的权力的野心家。在一个诸侯国之内,即使权势最大的贵族家族也不能保证不被摧垮,它的首领也很难避免受到谋杀的可能。不用说,普通大众的处境就更为悲惨了。在国与国和贵族与贵族之间,无论谁在争斗中获胜,普通百姓都得遭殃。甚至在和平时期,普通人也没有安全保障。他们无权无势,始终是贵族们的牺牲品。在这种朝不保夕的形势下,世袭贵族的主要兴趣自然就转向了狩猎、战争和穷奢极欲。为偿付这些消遣和糜耗所需要的费用,他们对人民的赋敛已经超过了人们最大的承受力;而对于人民的所有抗争,他们都予以无情镇压。
目睹这种状况,年轻的孔子根本不能忍受,他下决心倾尽毕生之力去匡正时弊。他坚持不懈地向人们讲述他的主张。根据他的主张,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适合于人们的生存。孔子逐渐召集起一群年轻人来学习他的学说,因此,他就成为一位知名的教师。
孔子学说的基本点是简明的。在他所见之处,人们都在彼此争斗,但他不相信这是社会的本有状态。他认为,人们彼此合作才是正常的;竞争是必要的,但竞争不应该是相互谋利,而应该是增进共同的福祉。在他看来,用来衡量统治者治国成就的标准应该是:统治者不是为自己敛财和攫权,而是设法给他们的子民带来福利和幸福。
孔子认为,只要仁慈的君主掌握政府,他梦想的世界就会到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孔子将乐于看到世袭制被废除,如果这一天真有可能到来的话, [5] 但实际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作为对这一理想的现实折中和替代,孔子转而努力说服君主们改变其管理机制,让他们的大臣有德行、有才能,以及经受适宜的从政训练。他努力教育年轻人做这样的大臣。因此,在他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中,孔子对贫贱者和富贵者一视同仁。孔子收授弟子只有两个条件:聪慧和勤奋。
孔子试图完成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他想取消统治者继承而来的实权,把它交给合乎道德标准的大臣,进而使政府改变其目标,从为少数人谋福祉转向为全体人民谋福祉。他明白,要完成这场革命,仅有思想信念是不够的,他还得努力激发弟子们对这一事业的真正热忱,而他自己的一生就是献给了这一事业。在这方面,孔子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个“有道之士”[Knights of the Way,借用阿瑟·韦利(Authur Waley)的妙语]的团体受到了这种献身精神的激励,而这种献身精神并不逊色于出现在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的骑士精神。
【按: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的骑士精神就是舔狗精神和疯狗精神的有机结合,也配用来和士人精神比吗?夷狄也配与中夏相提并论吗?】
然而,孔子并不只是要全力以赴地做个教师,他更想指导国家政治,并看到他梦想的世界在他手中变为现实。可是,当时的各国君主显然不可能认真考虑并授他以实权。尽管至多他们认为孔子是个无害的怪人,但是,一旦给他权力那就危险了。相反,他们把政治高位给予孔子的某些弟子。正是在这些弟子的坚持下,孔子最终在他的故乡鲁国得到了一个职位,但那只是个荣誉头衔,可能根本没有实在的权威性。 [6]
【按:在孔子从政的问题上,顾立雅的观点有很多错误。鲁定公重视孔子,支持孔子堕三都。鲁定公十二年,孔子为鲁国的大司寇兼摄相事,为了加强君权,派子路堕毁三桓的三都私邑。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显然是支持加强君权的,虽然君权也要被限制在礼法规定的范围内。鲁哀公作为鲁国君主称孔子为尼父,但是孔子年龄大了,不适合再担任要职了而已。显然不是鲁侯不愿给有实权的高位。】
当孔子发现在这样的位置上无所作为时,便去周游列国,寻求能够认真履行他的政治思想的在位者。但是他从未知遇。这样的游历持续了十多年。总的来说,周游列国期间的孔子几无所获,但却证明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信念而情愿备尝艰辛。
回到鲁国后,孔子继续其教学活动。5年之后,孔子去世了。他的一生没有大的起伏。没有高潮,也没有低谷。他的主要抱负无一兑现。在他去世之时,每个人肯定都认为他是个失败者。的确,他自己亦持如此看法。
孔子死后,在他的学说代代相传的同时,儒家也渐渐壮大起来,并不断扩大其影响。孔子的学说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阐释,逐渐发生了深刻变化,直到最后连他自己恐怕都无法辨认。但是,孔子所坚持的两项原则还一直保存着,即强调不是以出身而是以德行和才能为标准来选择从政者,以及政治的真正目的是人民大众的福利和幸福。尽管战争和压迫与日俱增,人民的生活日益维艰,但后一项原则却使得儒学在普通大众中广为传布。
西元前221年,相对野蛮的秦国蹂躏了中国,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极权帝国。儒生们拒绝合作,秦帝国就禁止了他们的书籍和学说的传播,甚至还处死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可是不到20年,一场革命就推翻了秦王朝,而儒士则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按:例如孔子八世孙孔鲋是陈涉的博士,坚决反秦!】
随后建立的汉朝总的来讲比较看重儒生。可是到了第六代皇帝,即怀有极权野心的汉武帝时,一些儒生与这个皇帝发生了冲突。汉武帝极其聪明,他没有公开反对儒学;相反,他摆出了赞助和拉拢儒学的姿态。他让一大批儒生享受政府俸禄,他还亲自主持朝廷选取官员的考试。可以说,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对儒家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大约从这时起,儒学开始被滥用,以至于发展到替专制政治作辩护的地步。儒学的这种转向,是对孔子学说的彻底败坏。然而,正是为了反对这种败坏,才启发和鼓舞了另外一些儒生的从未止息过的抗争。
现今流行的大部分有关孔子的资料出自汉代或汉代之后。孔子的传记和有关的注释确实是力图把肉和血附在古代典籍的骨架上。几乎在孔子去世之前,粉饰他的传统就开始了。孔子的那些非常重要的思想在他自己的时代并未受到赏识,而后来出现的孔子传记却把他写成一位有权有势的政治家,这种情形着实令人不可思议。另外,与儒学相敌对的思想派别起初是攻击和嘲弄孔子,但后来却又转而利用他,甚至是极权主义的法家也顺势把孔子变成了极权主义者。这方面最有效的做法是,法家人物借孔子之口倾吐极权主义观点,同时,为了掩盖对孔子思想的歪曲和利用,还在他们的著述中插入了一些最受人尊敬的儒学经典的字句。
对于那些认为孔子的民主观点难以接受,而要把他描述为肆无忌惮的帝国权威的支持者的人们来说,上述的一切是有用的。他们希求的只是把这些虚构的附加物设定为孔子的学说,并解说给其他人,从而使人们忘掉孔子其余的思想。这样,他们就建起了一层隔阂,使人们2000多年来难于发现孔子的真实思想。
可是,真正有辨识力的学者迟早都会出现。事实上,在17世纪和18世纪进入中国并成为学者和朝廷官员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就是这样的学者。他们拂去堆积如山的近代解释的尘封,力图还孔子以真实面目。他们在发回欧洲的一封封信函中,向人们讲述了他们所发现的这位令人鼓舞的“新”哲学家的思想。
因此,在欧洲,正当众所周知的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逐渐获得了名声和美誉。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Leibniz,1646—1716)、沃尔夫(Wolf,1679—1754)、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士,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进他们各自的主张;当然,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也受到了孔子思想的影响。在法国和英国,人们认为,在儒学的推动之下,中国早就彻底废除了世袭贵族政治,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武器攻击这两个国家的世袭贵族。在欧洲,对于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思想的发展,孔子哲学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的影响,孔子哲学又间接影响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有趣的是,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曾提议,作为国家的“政治拱顶石”, [7] 应该比照着中国的科举制度建立一种教育体制。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儒学对西方民主发展的贡献经常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所忘却。为此,我们必须检视儒学在西方民主发展过程中所发挥过的适当作用。
在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孔子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前辈。孙逸仙曾说:“孔子和孟子是民主的倡导者。” [8] 他还制定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华民国宪法》。然而,他的一些同胞至今还认为孔子是个保守主义者,认为正是孔子帮助统治者锻造了专制主义的枷锁,从而对孔子怀有敌意或冷眼相向。
在一本完全是论说欧洲的书中,里克(W. E. H. Lecky)的一番描述颇为适合孔子的情形:
在一定时代的思想基础上才能产生天才人物,同样,只有在一定时代的道德水平上才能产生这样的人物:他们预测并促进未来的道德水准,传布诸如德行、博爱或自我克制等等与他们的时代精神了无干系的道德观念。他们反复灌输种种义务,指点多数人都认为是完全空想的行为的动机。他们的完美无缺的道德魅力强烈地影响了他们的同代人。在这种热情的激发之下,一个追随者团体形成了,许多人从他们时代的道德状况中解脱出来。然而,这种运动的全部效应只是暂时的。起初的热情开始渐渐衰退,周遭环境恢复了它们的优势。尽管纯洁的信仰变成了现实,但却被装饰以异化了的、脱离原位的和扭曲了的观念,直到它起初的特质消失殆尽。曾是不合时宜的道德信条,一旦迎来与之适合的文明的曙光,就会发挥它的作用;或者至多是通过信条累积的微弱的和不完全的过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它所需求的环境的到来。 [9]
这一切均与孔子的情形相吻合。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正如他自己所言)孔子在世时无人完全理解他,以及后人为什么经常严重地误解他。它也有助于说明这样的事实:这个生活在很久以前的人物,在其有生之年默默无闻,却在身后留下了辉煌,并继续影响着甚至是现代人的思想和行为。
【按:孔子在世时就是被称为圣人了,怎么能算默默无闻呢?】
第二章 研究孔子的依据
人们经过很长时间才认识到,关于孔子的传统说法,即使许多学者能够接受,其准确度也是成问题的。1100多年前,生活在唐朝中晚期的最著名的儒者之一——韩愈,就抱怨同代人只是重复着关于孔子的一些极其乏味的东西。因此,他问道,如果有人想了解实情,“他们将从何处寻找呢?” [10]
几乎每个孔子的故事都以写于西元前100年左右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传记)为根据。一位西方学者曾写道,实际上这部传记“确定了所有时代孔子传记的基础”。 [11] 然而,19世纪初伟大的批评家崔述却尖锐地指出,这部传记事实上“十之七八是诋毁之语”。 [12] 一位当代中国学者详尽地研究了这个难题,认为在《史记》所有篇章中,这部孔子传记“最芜杂无条理”,以至于任何称之为作家的人都不会写成现在这种样子。 [13] 不过,无论这部传记有多少不足之处,它仍然是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起尽量可信的有关这位圣人的生平记载。
如果我们想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实情,就必须从新的角度研究这个难题。因为现存唯一完整的孔子传记(《孔子世家》)写成于他死后的几个世纪,所以习惯上就得从它开始,但却要努力剔除掉那些明显荒谬的东西。可是,即使这样做了,也不能保证余下的东西就是真实可信的。一旦有人成为孔子那样的文化英雄,他的名字就会出现在无数的故事中,这些故事根据的是讲述者的信仰和渴望,而不是英雄人物的生平事实。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基督教的传统说法的例子。正如保罗提醒我们的,大多数早期基督徒是卑贱之人,被人轻视,遭人迫害。当他们的孩子遭受同伴的欺辱时,一些父亲用来自我安慰的想法是:孩提时的耶稣就富有神圣的力量,不会任人欺凌。于是,有两部《天启福音》就说,当其他孩子冒犯年少的耶稣时,他就使用超自然力当场置他们于死地。 [14]
【按:杀人不眨眼的耶稣确实符合洋人的内心深处的渴望~】
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些故事呢?我们要把它们作为真实的历史吗?我们应该说它们是过分的并把被杀死的孩子的数目减少到一个吗?我们将排除超自然因素,并说这个孩子纯粹是自然死亡的吗?我们将更进一步认为,耶稣完全不是有意杀死孩子的,而这种事件无疑是根据他偶然杀过人的事实而生发出来的吗?显然,所有这些假定都是无谓的。我们越是努力变更这些故事以便使它们更可信,就越减少了彻底理解其原委的机会。其实,它们出自悲惨的、被压迫人民的白日梦。而只有这样加以理解,它们才具有实在的意义和引人注目的历史价值。但是,假如一定要从这些故事中引出耶稣的生平事实,我们必入歧途,因为它们与耶稣的所作所为绝无干系。
大多数孔子的传奇故事都与他本人无关。如果我们把诸如此类的故事放在其应在的位置上并仔细加以研究,它们将告诉我们大量的关于它们出现的那些时期(无论是汉代或其他时代)的人民的生活状况。但是,如果我们想从大量的孔子传奇中归整出孔子的真实生平,那简直是毫无指望的。因为,当传奇出现时,孔子已谢世300年或更多的时间了。那些传奇是极其混乱的,而且人们也没有区分其真伪的贴切标准。
所以,我们要依靠两种其他类型的材料来努力寻找真孔子。首先,尽管我们并不漠视在相对近晚世流行的种种传统说法,但我们认为它们只具有次等的价值,或者说是第二手材料,而我们主要依赖的是产生于近可能接近于孔子那个时代的有关他的记载。我们将把基本的参考资料限定在孔子去世后的200年内。其次,在每个主要观点上,我们将格外留心这样的作品:它们描述的是孔子时代之前的形势。
研究孔子之前的材料的重要性有时被忽略了。但是,如果我们确实要了解孔子是哪种类型的人物时,这种材料就是必要的了。我们举一个现代的例子。比如说,要想了解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为什么倡导每周工作48小时,除非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假如他生活在20世纪中叶,在一个许多人认为每周工作40小时就是标准的国家作如此倡导的话,他就是在主张延长周工时,而有人就会称他是个“保守分子”了。但是,如果他提出这一主张针对的是19世纪初许多国家盛行的状况,他就是提倡剧烈地缩短周工时,在那时,他的确会被称作“危险的激进分子”。
同样的,孔子曾说过他的一位弟子(冉雍)有资格登上诸侯国君主的宝座。 [15] 但是,我们仅仅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了解所有的背景。而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了孔子讲这话时的政治形势,那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这位弟子并不是世袭的君位继承人,并且有暗示说他的家世在一定程度上有污点。 [16] 然而,孔子却说,弟子冉雍所具有的德行和才能,使他完全可以去做国君。在汉代,这种说法并不稀奇,但在孔子之前的任何时代,从远古文献和青铜铭文(金文)的记载来看,世袭权力一向被认为是做天子或诸侯的唯一资格。 [17] 很清楚,孔子对这位弟子的评论并非草率的赞词,而是宣布了一项最重要的革命性的政治原则。
在描述儒家思想出现之前的中国的基本状况时,我们使用的典籍是众所周知的《诗经》、《易经》中的真正早期的部分、 [18] 《尚书》、 [19] 《春秋》以及传世的铭文。我们也将使用著名的史书《左传》,但是,现存的《左传》只记载到西元前300年左右,所以我们必须慎重使用它。 [20]
我们理解孔子生平和思想的基础是《论语》。这本书记载的主要是孔子师徒的言论。尽管并非整部书都是真实可靠的,但是,那些后来附加的部分却以种种方式经常不自觉地暴露出来。毫不稀奇,在文体、词句和思想上,《论语》的后加部分与真正的早期部分是很不同的,它们中的一部分甚至是由儒家圈子之外的人伪造的。许多学者于此多下功夫。本书“附录”概括了他们的成就,并详细讨论了《论语》各篇章的可靠性。
以哲学家墨子命名的那部书多处提及孔子。乍看上去,这部《墨子》应该是一种有益的资料,因为墨子生活的时代稍后于孔子。但是,许多批评家已经指出,论及孔子个人的那些内容多半是后来掺入《墨子》之中的。 [21]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孟子》是很有价值的资料。儒家哲学家孟子在孔子去世后一个世纪降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部书以早期的文体颇为详细地记录了孔子的一些言行,这些记载与人们所认为的《论语》早期部分的记述大体吻合。《左传》很详尽地记录了孔子在世时他的故乡鲁国的历史,但总的来说对孔子的生平却所记甚少。其中记载的许多事实说明,孔子在其有生之年并不像后来传统说法中所再现的那样是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左传》之中孔子的一些故事与其他的早期记载不一致,在某些记载中甚至出现了神怪或超自然的东西。根据这样的事实,以及《左传》之所记已经下至于西元前300年左右,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说《左传》中有关孔子的记述只能有一部分是值得信赖的。可是,这部分对于我们完整地了解孔子的生平却是很有价值的。 [22]
总之,在有关孔子生平的记载方面,孔子死后几百年写下的著作比那些完成于接近孔子时代的书有更多的细节描写,这与我们希望的正好相反。显而易见,那些大量附加的细节来自想象而不是事实,当我们审视儒家神话的成长过程时,将会留心这一部分晚出之书。 [23]
第三章 孔子时代的中国
要想理解孔子,必须认识他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有人指责孔子对政治事务太感兴趣,以至于他的思想看上去索然无味,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孔子力图给混乱之世带来秩序,他没有必要找寻使生活更有趣味的道路。在当时,要想坚持他的变革思想,并让人们像他那样自由地谈论它们,孔子是要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的。人们经常引述孔子对各种各样的贵族和君主所做的不厌其烦的学究式的说教,言下之意是说孔子言而不当。然而,一旦了解了孔子进行这种批评的背景时,我们就会明白,尽管这样的批评只是对于那些权贵们的缺点的责备,还不是对于他们的罪恶进行谴责,他们就坐不住了,以至于对孔子被折磨至死也并没感觉到应有的良心责备,竟如同对一只被压扁的苍蝇一样。
在孔子时代,中国正好站立于十字路口。现在,让我们简要审视一下他到达此处的进程。
考古学证明,与现代中国人有关联的上古之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生存了相当长的时间,可是人们关于中国历史的实际知识仅仅开始于西元前14世纪的商朝,它建都在现在的河南省北部。尽管我们只是从出土文物和一些简短的铭文中了解这个王朝的,但有证据表明,它显然已经达到了相当文明的程度。它的许多制造品显示出了高超的工艺,而它的青铜器则位列人类最具艺术性的工艺品之中。 [24] 这个文明未被摧毁,但却因为受挫而被延缓了。根据传统编年史的记载,在西元前1122年, [25] 一个相对野蛮的部落联盟征服了商朝。这些部落位于当时的西部,即现在的陕西省一带。这群征服者由周人率领,最终建立了周朝。立国之后,这些入侵者继续扩大他们的征服范围,直到占领了北部的大片地区。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用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管理这块领土,因为他们缺乏管理一个大国所必需的良好的交通状况、有效的金融体系和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
因形势所限,这些征服者不得不把大半领土分割成块,分配给周王的亲戚和协助周王进行征服战争的其他部落首领。这样就产生了封建制。在这个制度下,每个封国的君主(诸侯)可以随心所欲地管理自己的领地,只要不扰乱王朝的和平。他们要定期向周天子纳贡,并在需要时参加天子的征战。
在孔子时代以及稍后时期,早期周朝被描绘成一幅几乎是中国人的理想时代的画卷:天下一统,和平而公正。而我们从当时的青铜铭文中得到的较为真实的描述则说明,那幅画卷是被严重夸张了的。不过,相对来讲,除了强制性外,可以说周朝已经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政治道德水准。因为周朝东部的诸侯被虎视眈眈的强敌包围着,这就一方面迫使诸侯们服从天子的领导并相互合作,另一方面又限制了他们过分压迫属地内的人民。事实上,如果周朝要保持住他们的统治地位,就不得不去赢得人民的支持。
在周人的种种政治作为中,有一场宣传运动颇为重要。这种宣传把周朝的征服说成是利他主义的讨伐,其目的只是要解放东方的人民,因为这些人民生活在“不道德的”的压榨者的统治之下。为了让人们接受这种设定,周王朝提出了一种关于中国历史进展的新说法。 [26] 他们宣称,周朝之前的夏朝和商朝的开国之君是表现良好的,但到了王朝的最后时期却出现了不道德的暴君。每当这种暴君当政之时,首要之神——“天”,就会四下寻找一个有资格重新接受“天命”的贵族,一个通过起义建立新王朝的受命者,这就产生了“革命有理”的理论。据此理论,这个受命者不仅有合法的权利,而且有神圣的义务去推翻暴君。如果有人要问:如何将纯粹的犯上作乱者与上天指定的王朝合法继承者区别开来呢?回答是:人民将追随后者的事业,并协助他取得胜利。很清楚,尽管周朝的宣传家并没有明显的政治民主的意图,但却为后来的民主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王朝的权威开始衰减,第一代封建诸侯的后代们再也不受相互合作之规定的约束了。他们逐渐无视天子的号令,彼此征战不休,以至于强大的邦国开始吞掉弱小的近邻。西元前771年,也就是孔子诞生前220年,由几个诸侯和一些“蛮夷”部落组成的联盟进攻周朝西部的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周天子(幽王)被杀,西周王朝完结了。继位的天子(周宣王)迁都到东部的洛邑(今河南洛阳)。这就是周朝后期称为“东周”的由来。建都洛邑的东周王朝总是处在某位诸侯的保护之下,从此以后,周天子基本上只是诸侯首领的傀儡了。
环绕中原诸国的所谓“蛮夷”部落并不一定是不同种族之人,区别只是他们没有履践中原的华夏文化。几个世纪过去后,他们多半都在渐渐中原化,变成了中原人,但在此之前,他们却是一种经常性的威胁,不断地在边境一带抢劫,并伺机吞并中原诸侯国的领土。政治分裂使得中原诸侯国无力抵御这些“蛮夷”之人的侵蚀,但有一种倾向越来越明显,即如果华夏文化不想被灭亡,就得有个领袖人物出面主持大局。然而周天子软弱无能,根本无力担当盟主的角色。在诸侯国中,尽管有一些君主很想称王称霸,但是,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强大起来并对他国形成威胁时,其他诸侯国就会群起而攻之。不过,到了西元前679年初,东周诸侯国还是拼凑起了一个同盟,同盟中最有力的诸侯(齐桓公)领起“霸(伯,贵族首领)”的头衔。在随后两个世纪里,还有几个诸侯担当或自诩过这个头衔。他们强有力的时候,就向承认他们领导的各国征收贡赋、监督共同防御,并取代了除宗教职能之外的所有的天子之事。
在东周初建(前770年)与孔子诞生(前551年)之间的200多年里,各国疆界不断变更,其情状只能用简图(见前附)的方式大概描述一下。总的来说,在中原地区的中心地带,黄河两岸的国家保存的华夏文化是最近乎纯正的传统。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周王的皇家领地、由商王的后代统治的宋国以及宋国东北面的孔子故乡鲁国。这些诸侯国以及别的中央小国,与周边国家相比,长于文化素养,而拙于武备和军事扩张。中部诸国产生的思想家倾向于强调和平与人的幸福,而许多尚武者和“律法”者(兵家和法家人物)却是周边国家之人。
尽管南方大国楚国几乎统治了整个长江流域,但是经常不断的国内贵戚间的明争暗斗却削弱了它的巨大潜力的发挥。在文化上,楚国与中原诸国有一定的隔阂。如上所述,楚国本来是“蛮夷”之邦,它只是逐渐成为华夏文化的信徒的。
楚国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符合西方大国秦国的实际。秦国建都在现在陕西省西安市的附近,这是周人的故址,但有证据表明,秦国文化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整个中部诸国的华夏文化,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不同,后来才促进了秦国的极权主义的成长。
还有另外两个强大的国家,即建都在现在山西省的晋国和包括现在山东省大部分地域的齐国。齐国既富庶又有实力,齐桓公率先夺得霸主地位,除了名号和宗教职能外,他几乎取代了周天子。但是,为了保住他的霸主称号,齐桓公不断进行军事征战,直到把齐国的国力消耗殆尽。齐桓公在西元前643年去世,此后,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王位而大动干戈,掀起内战。齐国就此衰弱了,以至于在此后的诸侯联盟中从未再掌握过显著的权力。
没有必要详细复述这一时期几乎连绵不断的战争,不仅中原各国彼此兵戎相向,还有半野蛮的楚国的不断加入。而且,此时的北方“夷狄”之人也经常对中原地区进行威胁。有一次,在位的周天子请求狄人帮助他对抗中原之敌,结果是,周天子本人有一段时期却被这些狄人逐出了都城。一般的模式是,几乎总是周边的大国之间发生不断的军事冲突。中部小国情愿保持中立,但那是行不通的。他们被迫依附这一边或那一边,而当新的压力出现时再变换立场。他们最不幸的事实是处在大国之间,成了命中注定的相邻强国之间的战场,有时甚至是定期的。因此,周边大国省去了战争的恐怖,而中部诸国却大遭其殃。中部诸国的哲学家之所以大声疾呼和平,而周边地区的哲学家之所以倾向于赞美战争的荣耀,以上所述无疑是原因之一。
有时,大国的军队并不互相攻击,而是仅仅满足于惩罚中部诸国的摇摆不定,并迫使他们发誓忠诚于新的协定。协定的签署完全是一种宗教仪式。先要宰杀一个用作祭品的动物(“牺牲”),把它的血涂在协定的每份副本上。参与协议的每位国君或官员在签署协定后大声朗读它,并把牺牲品的血涂在自己的唇上。最后,一份副本与这个牺牲品一起埋掉,以使神灵能够强制协议条款的实施。孔子出生前几年就有这样一个协定,内容是强迫中部国家郑国加入诸国联盟。这份协定的结尾是这样说的:“如果有谁毁约,那么那些负责监督签约者的忠诚和协定执行的人、著名山河(的神灵)、众多的(其他)神灵和所有接受牺牲品者,以及我们七姓十二国的祖先——所有这些精明的神灵,都会来惩罚他,使他失去他的人民,还要废除他的职位,惩治他的家庭,完全毁灭他的国家和家族。” [27] 这真是太可怕的誓言了。然而,两个月之后,在武力压迫之下,郑国就又一次改变了它的忠诚。
其他国家也受难于这种情势。但是,像郑国那样被迫向新主子发誓永远忠诚的习惯性做法变得那样滑稽,以至于类似郑国的这种宣誓效忠的做法几乎毫无意义,所以,郑国索性就把它的宣誓效忠不再指向某个特定的国家,而是任何有能力提出这种要求的国家。 [28]
具有这种时代特征的国家事务对当时人们的思想有两方面的重要影响。首先,这些国家显然是经常因为惧怕惩罚而加入同盟,旋即又在适当的时机退出,但是,这些改变立场的国家并没有遭受到应该行使打击作用的神灵的惩罚。实际上,真正受到武力惩罚的正是那些尽力对他们的协定保持忠诚的人。所以,在这一时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怀疑主义,并逐渐怀疑到了神灵的存在,更别提这些神灵发挥其力量了。其次,不仅是宗教,就连伦理道德的基础也受到摇撼。无论何时何地,武力和强权就是正义。不仅是每个正常人,就是傻瓜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孔子的故乡鲁国相对弱小一些,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国家却未被任何大国摧垮和吞并,并且一直坚持到周朝末年。形成这种结局的部分原因,可能因为鲁国是著名的周公(旦)所建。周公是周王朝建立者(周武王)的兄弟,而鲁国则被看作是古代文化和礼仪的博物馆。某个强国要灭亡鲁国并非难事,但要真的这么去做,却得担负不太好的名声,明显得不偿失。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国家的日子就很好过。事实上,它也经常为各种内忧外患所困扰。可是,与更靠近中心地区的国家相比,鲁国所遭受的战乱之苦更少一些。詹姆斯·理雅格(James Legge)统计出,在《春秋》所记载的年代里(前722—前481年),鲁国只受到过21次入侵。 [29] 与这一时期其他中小国家所受到的攻击相比较,这显然是很少的。
齐国是位于东北方的大国,也是鲁国的祸根。鲁国与齐国之间的战争是相当频繁的。齐国经常蚕食与鲁国接壤的领土,而鲁国则不断奋起抗争。有时,鲁国的反抗也会取得成功,甚至还能夺回部分领土。不过,鲁国要想真正有效地抵御齐国,只能求助于其他大国。早在西元前634年,鲁国就曾请求南方蛮夷之国楚国帮助其抗击齐国,并且真的获得了援助。 [30] 西元前609年,齐国支持的一个鲁国大臣谋杀了鲁国的两位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并让一个鲁君姬妾的儿子做了鲁公。 [31] 这位鲁公在位期间,齐国一直控制着鲁国之政。在这种情况下,鲁国最终不得不请求晋国的援助,以使其脱离齐国的左右,重获独立。从此以后,鲁国也就成了强国的随从。然而,这并不是说鲁国就完全是个可怜的受害者和无辜者。在大国面前战战兢兢的鲁国,却在比它更弱小的国家面前耀武扬威,侵略、惩罚和吞并,能做即做。
鲁国的内政呈现出与其他国家一样的特点。在整个中国,各个封建国家都是通过牺牲周天子的利益来扩大自己的权力,直到把周王降为傀儡。在封建邦国之内,则风行的是诸侯的大夫想方设法篡夺国君的权力。
在阅读儒家的《论语》时会遇到“三家”这个词,它指的是三个贵族大家族,他们是鲁桓公(前711—前697年在位)三个儿子的后人。 [32] 这三个儿子被称作孟、 [33] 叔和季,即老大、老二和老小这兄弟三人。正如欧洲的童话故事一样,最小的总是最成功的。这位季氏家族的奠基人(季友)反对他的残暴兄长(庆父)的计谋。作为老大家族之奠基人的庆父,试图自己登上君位。季友与之抗衡,还挽救了鲁君合法继承人(鲁僖公)的性命。作为奖赏,季友成了鲁国的上卿(宰相),大权在握。从这时起一直到孔子时代,鲁相的位置一直成功地掌握在季氏首领(季孙)手中,尽管其间也有一阵子被其他变得更有力量的家族暂时拥有。
大约在孔子出生前的150年间,鲁公的权力大部分落到“三家”手中,“三家”也逐渐加紧了他们的控制。其中两家的首领(孟孙和叔孙)参与了对两位鲁(文)公继承人的谋杀,并在西元前609年把他们更能接受的继承人(鲁宣公)扶上了国君的宝座。西元前562年,“三家”瓜分了鲁国,包括国家的军队和大部分岁入。他们留给鲁公的东西微乎其微,唯一得到保全的只有举行各种国家礼仪的特权。西元前537年,即孔子15岁时,季氏占据了半数以上的国土,孟氏和叔氏则占据了十分之四,而鲁君所能获得的收入只是“三家”高兴时给的一些贡物。 [34]
当然,在“三家”逐渐夺权的过程中,历代鲁公并不是没有做过从这种控制中挣脱出来的努力。孔子34岁时,鲁昭公带领一伙人企图杀死季氏首领(季孙),但在最后一刻却让他侥幸逃脱了。当双方面临决战时,叔氏搭救了季孙,鲁昭公被迫逃到齐国,在那里过起了被放逐的生活。 [35] 季氏只是定期送马匹、衣服和鞋子给鲁昭公和他的随从,但不允许他们返回鲁国。7年之后,鲁昭公死在国外。这次对抗,是鲁公坚持其独立性的无数次企图中的最引人注目的一次。
很自然,其他贵族们对大权在握的“三家”也会产生嫉恨。他们之间常有争执,起因则是多种多样,诸如与女子的私通,有一次甚至是为了斗鸡中的一方给鸡爪子装了个铁刺。这种争执通常导致暴力。反对“三家”的贵族们常用的借口是,要使鲁公重新获得被篡夺去的权力,但是“三家”牢牢掌握着权力。有时,“三家”之间也有争吵,但他们足够精明,认清了他们之间必须合作,否则就要面临灭顶之灾。
正所谓上行下效,周天子被篡权的进程也就是诸侯被篡权的进程,诸侯的权力被他们的卿大夫篡夺,但是,这种进程并无休止。这些卿大夫的属下(家臣)也在竭尽全力侵夺上司的权力。当这些家臣作为邑宰掌握了某座城邑时,有时会关起城门据邑叛乱,背弃对上司的忠诚。有时,据守着这些城邑及其所属地域进行叛乱的家臣,还会把这些地盘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
孔子47岁时,季氏的家宰(总管)阳虎进攻季氏并囚禁了季桓子(季孙),还强迫季桓子跟他签订协议,以承认他的权力。第二年,阳虎又迫使“三家”的所有大夫以及国中的其他人与他订立盟约。此时,鲁国实际的统治者既非鲁公又非“三家”的首领,而是阳虎。两年后,阳虎与另外一些家臣策划谋杀“三家”的首领,也就是说,阳虎企图彻底地取季孙而代之。但是,这个计划却在最后时刻败露,阳虎也不得不出逃他国。
不仅是鲁国,别国亦复如是。几乎谈不上权威和秩序,只有不断的暴力消长。宗教仪式倒是大派用场,因为不断举行的订盟仪式少不了它。但是,楚国的一位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能从敌人那里获得利益,就要不顾盟约地勇往直前。” [36] 在这个时代,没有我们所谓的法律概念,而且处处都是一样,人的生命是廉价的。吴国的国君为了不走漏坏消息,便亲手割断了碰巧在场的七个人的喉咙。 [37] 被主人怀疑下了毒的食物要由狗和仆人来尝。 [38] 有个小国的君主是刀剑收藏者,他用属下的脖子试验新的收藏品。 [39] 晋灵公喜欢在塔楼上用弹弓射击行人,观看人们在他的弹丸之下东躲西藏的样子;厨师做的熊掌不合他的口味时,就会被他杀掉。 [40] 尽管这样的统治者是不常见的,但并非不常见的是,贵族们总是要威胁那些敢于劝止其行为的下属,并杀死那些苦谏不已的人。如果不便直接杀死,有时还雇用刺客。同样的,过度严酷的惩罚司空见惯。在齐国,断足之刑(刖刑)相当常见,以至于店铺里都要销售为这些蒙难者专用的特制鞋袜。 [41] 所有阶层都通行贿赂,从有利于某些人的司法舞弊,直到别的国家贿赂某个大国的权臣,以便得到有利的外交政策。
即使亲戚之间也互不信任。对统治集团成员间存在的信任程度,可以从吴王僚接受其亲戚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的一次宴请中得到证明。那时,孔子大约30岁。公子光想在宴会上杀死吴王僚并取而代之。他做了精心的策划,把刺客(专诸)藏在宴室下面的地窖中。吴王僚已有怀疑,但还是应邀前往,并做了周密的防备。他在沿途都布置了士兵,宴室内外戒备森严,站满了全副武装的亲信。吴王僚的这些亲兵把送餐的侍者挡在门口搜身,并要求侍者更衣,跪着上食,甚至侍者两旁还有带剑的卫兵随行戒备。这些预防措施看上去已经无以复加,但专诸却把匕首放在鱼腹中,爬行献鱼,然后突然抽出匕首刺死了吴王僚。而史书的记载则说,与此同时,“两柄长剑刺入了凶手的胸膛”。 [42]
齐国的两个有权势的家族敌视另外两个家族,他们听说对方要来进攻,便马上集合起属下,并分发了武器。准备停当后,他们去探查了敌方的情况,却发现情报是假的。然而,结果却是,为了防止对方在得知他们武装起来之后发动进攻,使自己陷于被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马上采取主动,抢先下了手。 [43]
正如有时人们所断言的,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孔子在伦理道德上的表现是极端拘谨的。尽管这种断言对孔子来说并不很公正,但是,他的许多同代人却连领受此种责备的资格都没有。在当时贵族们的种种非道德的表现中,私通甚至乱伦相当常见。女人,甚至是别的贵族的妻子,有时不经过任何礼仪就被那些权贵给占有了。
当然,也有一些事例表现出了这个时代特有的伟大忠诚。比如说,有许多豪侠为他们的主人和他们的原则而死,拒绝不义之所得。但是,与之相反者比较,这种道德之行真是太稀少了,并且有许多人物及其事件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并不可信。如果能作一些比较全面的思考的话,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某些混乱和不安定的观念可能来自这样的事实,即某些贵族,决不是想要得到更多的领地,而是有意把他们的一些土地返还给他们的领主,希望通过减少对土地的大量拥有使他们逃脱灾祸。 [44]
个人之间的严重缺失道德的特色也体现在了国家关系上。外交使节一定得是勇士,因为如果他出使的国家被他的国家惹恼的话,他本人就会有杀身之祸。即使国君对另一国进行友好访问时也难免被扣留,这种扣留可能是为进攻该国做准备,或是为了其他原因。例如,两个小国的君主曾被楚国扣留了3年,因为他们拒绝给楚国的令尹(宰相)送上他想要的珠宝、裘衣和马匹。 [45] 有一次,一位鲁公访问齐国时被拘押,直到同意将次女嫁给一个齐国大夫。楚国的一位君主听说一个小国——息国君主的夫人很漂亮,就派人传话说,他要去息国与息侯会飨。可是,一到息国,这个楚君就杀了息侯,灭亡了这个国家,最终把息侯的夫人息妫掳掠到了楚君的后宫之中。 [46]
贵族们缺乏足够的安全,人民则根本没有。他们主要是农夫,实际上就是农奴。他们没有任何力量对付贵族,事实上,他们面对的只有纳税、劳作、土地被征用、饱受折磨和被贵族杀死。劳作者的这种遭遇几乎是无法阻止的,所以到了受苦至极时,他们只有造反。可是,对于不成功的造反的惩罚,必定是把造反者拷打至死。
即使显贵们在他们的领地之外四处游逛时,也像蝗灾一样穿过农田,伐木做薪,踏平庄稼,毁坏房舍,回去时还用武力“要求”贡品。这些暴行,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常有之事。然而,连绵不断的战争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比如,西元前593年,宋国的都城被长期围困,以至于居民们饥饿难耐,被迫去吃小孩子。因为不忍心吃自家的孩子,便“易子而食”,相互交换着去吃。 [47]
周朝中央集权政治权威的逐渐崩溃越来越加重了人民的苦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的数目却增加颇快(这部分要归因于多配偶制)。与此同时,即使是低等贵族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奢侈。在偌大的中国,支撑一个王宫的挥霍并没有多难,但是,当大批的诸侯都想如同天子一样地过着无度的生活时,经济就会很紧张。如果卿大夫和他们的家臣们也都要努力保持他们不加节制的优渥的生活方式时,大众的赤贫就势在难免了。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为了维持他们的体面,贵族们不得不发动多种多样的国内的、族内的甚至私人之间的战争。这样一来,社会情势就必然会一步步地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了。
这种社会机体内部的疾病逐渐产生出了它自己的抗生素。理论上讲,贵族所有的儿子都应该得到封地和在政府中职位。但是,随着岁月的飞逝,贵族祖先太多了,以至于这个理论实在行不通了。结果是,即使国君的一些近亲都沦落为穷人。 [48] 而在日积月累之下,社会上就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有着高贵的世系,多半还受过教育;他们虽然称得上是贵族,但却很贫穷,其实际的社会处境近乎普通人。
所以,至少是作为先例,正是这样的破落贵族后裔组成了贫困的士阶层,他们在周朝后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武士和待雇的刺客,另一些是各国朝廷里的官员和小吏,但是,他们之中也有一些是哲学家。这样的哲学家毫无例外地是些愤世嫉俗之人,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更好的东西,或者至少是其他人认为他们应该具有如此的见识。总之,他们不想接受现状。他们不是愚味无知的农夫,不会甘愿受苦而不抗争。他们对自己所受的压迫显然不满。而在他们之中,就有那么一些怀有利他主义思想的人,信仰的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孔子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注释
[1] ——译按:据《史记·宋世家》、《孔子家语·本性解》等,孔子的始祖是殷天子。
[2] ——译按:据《孔子集语》卷十三引《拾遗记·三》:“孔子生于鲁襄公之世,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来附徵在之房,因梦而生孔子。有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而来沐浴徵在。”“徵在”即孔子之母颜徵在。
[3] ——译注:《论语·子罕第九》:“吾少也贱。”《史记·孔子世家》(以下简称《世家》):“孔子贫且贱。”
[4] ——译按:《孟子·万章下》:“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世家》:“及长,尝为季氏吏,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
[5] 因为本章是概括全书的内容,正文中没有引证相关原典。相同的观点将在下文展开。
[6] ——译按:在孔子从政的问题上,顾氏在本书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也将在此后章节中顾氏具体讲到相关问题时再详加讨论。
[7] 杰弗逊,Ⅸ,第428页。
[8] 孙逸仙:《民权主义》卷一,第10、169、232页。
[9] 里克,卷一,第310页。
[10] 韩愈:《原道》卷11:“其孰从而求之。”
[11] 卫礼贤,第71页。
[12] 崔述,卷1,“《史记》之诬者十七八”。
[13] 钱穆,第40页,“余读《史记·孔子世家》最芜杂无条理”。
[14] 皮克,第96—97页。
[15] 《论语·雍也第六》:“雍也可使南面。”
[16] 见《论语·雍也第六》“子谓仲弓”章。事实是,《左传》中并没有提到过任何姓冉的君主之家,这显然排除了冉雍曾是君位合法继承人的可能性。就我所知,其他资料中也没有任何类似说法。
——译按:所谓“污点”,应该是指《论语·雍也第六》所说的冉雍好比是“犁牛之子”,即出身于社会下层。
[17] 尧传位给舜的根据当然不是家族继承权,根据传统说法,尧在生前就把王位禅让给了舜。但最近的研究表明,不仅这些帝王纯属传奇人物,而且讲述他们以德禅让的著作也是成书于孔子之后的。详见原书第186—189页。
[18] 亦即《易经》的卦辞和爻辞,不包括所谓“十翼”。“十翼”的出现晚于孔子,这些将在下文讨论。
[19] 对《尚书》的详考,见顾立雅,第55—89页及第111页注[1]。《尚书》中的下列篇目我认为无疑是儒家之前的,它们是《汤誓》、《西伯戡黎》、《微子》、《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君奭》、《多方》、《顾命》、《费誓》、《文侯之命》和《秦誓》。还有几篇可能与孔子同时,但必须留在怀疑之列。余下的亦即组成今文《尚书》的大部分,明显是后来的伪作。古文《尚书》并未提及,因为一般都认为(正如中国学者早已证明了的)它们是伪造的。
[20] 见原书第202—204页。
[21] 见本书注释 。
[22] ——译按:顾氏对《左传》的如此断言是有先入之见的,从《左传》全书的角度,有关孔子的记载确实分量不多,但是在《左传》记载的近300年(前722—前453年)的历史中,除了一些重要的君主之外,能够获得孔子般记载的人物并不多见,所以,在《左传》中,孔子无疑是重要历史人物之一。另外,对于《左传》中关于孔子的记载,顾氏又加以有选择性的肯定,这也只能使相关问题更为复杂。有关这方面的讨论,我们将在本书后文专门论说《左传》时再加深入。
[23] 古斯塔夫·哈龙(Gustav Haloun)出版了这种内容的三个主要文本,他称之为“前儒家的著作残篇”(“纬书”)。它们很有意思,但是根据其日期和内容,我们没有理由把它们视为研究孔子的基本材料。
[24] ——译按:其实最能代表商代文明的,是以甲骨文为表征的成熟的文字体系。
[25] ——译按:关于周人灭亡商朝的时间,学术界有多种观点。如《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武王灭纣在西元前1046年。
[26] 对这场宣传运动的较全面的讨论以及对于早期历史的不同看法,见顾立雅第47—95页和顾立雅(4)第367—375页。可必须指出的是,有人认为还有比《易经》更早的证据,表明周是臣属于商的,尽管正史的描述并不明确。
[27] 《左传·襄公十一年》:“或间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队(坠)命亡氏,踣其国家。”
[28] 《左传·襄公九年》:郑国子驷、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强是从。’”
[29] 理雅格译:《左传·哀公十二年》。
[30] ——译按:详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31] ——译按:详见《左传·文公十八年》。
[32] ——译按:因为是鲁桓公后人之故,“三家”也被称作“三桓”。
[33] 鲁庄公是次子。孟氏起先叫仲(氏),理雅格认为他是嫔妃所生之故。见理雅格译《左传》第74页。
[34] ——译按:在孔子时代,鲁公尚有自己的田地,《论语·颜渊》记载鲁定公与孔子弟子有子曾有过因为“年饥,用不足”而是否增加税收的讨论。只是鲁公田地甚少,甚至有时不足以维持其日常所需而已。
[35] ——译按: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36] 《左传·成公十五年》:“敌利则进,何盟之有?”
[37] 详见《左传·哀公十三年》。
[38] 详见《左传·僖公四年》。
[39] 详见《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40] 详见《左传·宣公二年》。
[41] 详见《左传·昭公三年》。
[42]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铍交于胸。”
[43] 详见《左传·昭公十年》。
[44] 梅,第176—177页。
[45] 详见《左传·定公三年》。
[46] ——译按:详见《左传·昭公十四年》。
[47] 详见《左传·宣公十五年》。
[48] ——译按:周天子权威的崩溃,贵族间的冲突,小国的灭亡,均可能产生这样的破落之家。
孔子
第四章 生平纪事
孔子的先祖是谁,我们无法确知。《左传》的确有过孔子的详细家族世系,但这并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记载。在论及孔子的先人时,这本书的细节未免太多了,以至于使人不得不产生怀疑,因为比《左传》更早的著作并未提及类似的细节。《左传》的这项记载中的其他地方也很值得怀疑,特别是认为孔子是商朝天子之直系后代的说法。 [1]
孔子出生在鄹地,这是鲁国的一个城邑,位于现今山东省曲阜西南部附近。传统上认为孔子生于西元前551年,这至少很接近事实。 [2] 没有一部早期著作提到他父母的名字。 [3] 这种情况支持了传统的说法:他很早就成了孤儿。对于他自己的家庭,我们知道的是,他有一位兄长和一个侄女,而他本人则是一子一女的父亲。 [4] 孔子在世之时,他的儿子(孔鲤)就去世了。至于他的妻子,我们却无从知晓。以上所述就是早期文献的记载。然而,后来的传统说法却为这位圣人附加上了君子所有的必备物,甚至包括休妻。 [5]
要确定孔氏家族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相当困难的。 [6] 孔子自谓“少也贱”,年少时地位卑贱。 [7] 这就说明,他显然也没有可观的财产。 [8] ——从《左传》上看,孔子是鲁国唯一的孔姓著名人士,尽管这个姓氏在其他几个国家大名鼎鼎,其中一个国家是宋国。传统说法认为,孔子的先人早在他之前三代就从宋国迁出。可是,这种说法是相当靠不住的。然而,孔子的祖先极有可能是贵族,但也只是低级贵族。那时的中国,从贵族降为“贫民”是瞬间之事,大世家的后代很可能就在耕种田地。 [9] 这并不是说孔子是农夫。他受过教育,还有闲暇追求诸如射箭和音乐之类的消遣,这就最好地解释了传统说法,即尽管年轻的孔子身处穷困之中,但却具有贵族的血统。
至于孔子受教育的过程,史料记载留给我们的几乎是一片漆黑。孔子弟子子贡说,他的先生“无常师”, [10] 意思是说,孔子没有固定不变的老师,但这并不一定说孔子是无师自通。孔子年轻时曾是从事文书杂务的低级官员,并且很可能因此而受到过正规的基础教育。孟子说:“孔子曾做过仓库管理员,他说:‘我的账目肯定是清楚无误的。’他也曾负责饲养牲畜,他又说:‘我的责任就是使牛羊肥壮。’” [11]
尽管孔子从不有意掩饰他卑贱的过去,但长大后还是觉得有些羞愧。 [12] 然而,没有这些早期的生活起伏,他就不可能成为那么伟大的人物。实际上,这些经历影响了后来整个中国的文化史。早年的奋争使孔子接触到了普通大众,并对他们产生了深切的同情,这种同情从未从孔子身上消失,并从一开始就使儒学蕴染上了这种色彩。正是普通人的处境使孔子拿定主意:就他所能做到的,要使每个有才能的年轻人都能获得有所作为的机会,而不要在意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多么卑贱。当孔子后来宣布在他的课堂上从不拒绝任何一个有大志的学生(无论他多穷),并断言每个青年都应该受到尊重,直到他们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时候, [13] 他便是既讲述了一位伟人的高尚原则,也(无疑是不自觉地)证明了他自己年轻时的奋斗目标是正确的。
孔子胸有雄心大志。因为他没有继承到有影响的社会地位,所以,他只得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它。然而,这并不是说他适合于从事任何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事情。在当时,最有指望的前途之一是政治阴谋,但是,孔子既无此能力,又无此天赋。即使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孔子也从来没有屈从于任何政治阴谋,孔子也不赞成为战争而战争。这就剩下了多种正统的出人头地渠道中的唯一路径,即设法赢得某位国君的欢心。但不幸的是,孔子对此更是一窍不通。
孔子从来就不会阿谀奉承。相反,当孔子的一些朋友颇费周折地使一位实权人物对孔子产生了好感,并撮合成双方的一次会面时,孔子却抓紧这种天赐良机去指出那个有希望成为他的政治赞助人的错误和克服错误的办法。这种做法是否有助于政府的道德进步并不好说,但它对孔子的政治事业却是无益的。进而言之,孔子并不擅长与“识时务”的人谈话。他不关心,也可能根本不知道如何避免愤懑之中的刺耳之言。不过,孔子的一些弟子可比他强,比如说像子贡这样口才非凡的弟子就被当权者所欣赏,并且能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这是毫不奇怪的。孔子经常责备辩才,以至于我们不能肯定但却怀疑他是否无意中羡慕那些拥有这种才能的人。 [14]
孔子在脾性上就不适合做一个现实政治中的成功者。就他的资质而言,孔子毋宁是个天才的哲学家和教师,而在其他许多方面,他的天赋与现实的要求刚好相反。年轻时的孔子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是,假如当时有人告诉他,他会强烈否认的。不过,即使他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年轻的孔子也并不明白采取何种正确的行动路线。孔子向往着两件事:第一,如同任何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样,他很想出名。第二,他想减轻他所看到的所有骇人听闻的大众的苦难。但是,仅仅怀有这样的抱负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是怎样依靠哲学和教育达到目的。
在孔子时代,只有去从政才能获得名声和在现实中取得实际成就。在那样的社会中,大部分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是由某些政治官员负责的,可它们只是这些官员们政务活动中次要的和附带的部分。这样一来,他们肯定不会做出多少像样的成绩。确实,负责宫廷仪式的官员必须得研究礼仪,而其他官员也会为了某个特殊目的而去查阅历史档案。但是,因为忙于日常公务,他们既没有闲暇全身心地研究与他们的职责有关的全部学问,更没有工夫平心静气地思考文化问题,而这些却是哲学家所应必备的,因为他们探究的是变动不居的宇宙现象的意义。
孔子做了所有的这一切。孔子力图获得有实权的政治地位,但是当这项追求彻底失败后,他便渴望得到闲暇,以便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化沉思。他多次拒绝“识时务者”的拉拢,因为他终于发现(并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具备与这种人进行周旋的才能。这一定鼓舞他加倍刻苦地做学问,以便在这个他根本碰不到真正对手的领域里卓越超群。当他悲叹自己求仕失败的惨痛时,做学问(以及后来的教学)自然就成了他的真正乐趣。在朝廷之中孔子没有用武之地,像一条脱离了水的鱼儿,直到生命的终结。但是,在弟子们中间,孔子却精神抖擞,如鱼得水。
孔子可能是他那个时代的最有学问者之一,但这不一定意味着他读过大量的书。首先,许多后来声称出自远古时期的典籍在孔子所在的时代尚未问世。其次,还有原本佚失、副本稀少和书籍流通困难之类的问题。那时,典型的书稿是所谓的“竹简”,写在竹板上,用绳子捆扎起来,类似于缩小了的栅栏。不用说,这样的“书”既笨重又制作粗陋,既不便于携带也不方便阅读。孔子熟悉一些历史文献,他也可能记诵了著名的《诗》三百篇,他也曾悉心研究了礼(我们可以说它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而之间的区别在那时无关紧要)。在他那个时代,礼存在的表现形式主要靠的是约定俗成,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它有多少内容能被记录下来。
尽管书籍给孔子提供了思想基础,但却并不是他的思想的唯一源泉。事实上,他有时毫不犹豫地用一种只能被称为毫不在意的方式解释各种书籍的内容,以便得出自己的论点。 [15] 因为从根本上讲孔子并不是学者,而是政治—社会改革者,他在寻求一种使他的世界从近乎混沌中解脱出来的途径。他相信政府就应该为全体人民谋利益。但是,孔子所取得的思想成就(从此以后成为儒学的基石)尽管灿烂夺目,但却并不是能够确保实现上述目标的特效良药。他深信,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必须由这样的人对政府进行持续不断的管理,他们应该达到最高的人格高度,接受过充分的政务训练,并且以此努力献身于公共福利,以至于必要时以死捍卫之。 [16]
孔子最终认定,自己才是能以上述标准去管理政府的最合适人选,这一结论是不足为奇的,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孔子深信,他的使命就是救世。 [17] 他以这种独一无二的方式去着手实现这一目标,在好多时候还几乎获得政府要职。后来,当这方面的努力最终失败之后,他转而去一门心思地从事教学。 [18] 有人认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人教师,这一点很难证明。但是,即使在孔子成名之前有过这样的教师,也在历史的演化中被孔子的名声淹没了。从《论语》中可知,在当时社会中,教育尚未被看作是一种职业。 [19]
孔子最初的学生可能只是个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集群。 [20] 后来成型的“儒家学派”大抵就是起始于这样的一个非正式的文化讲习社团。此可由一些弟子只比孔子小几岁这一事实来证明。 [21] 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孔子的思想品质和人格力量就使他被看作是夫子(师长)了。孔子的杰出之处是显而易见的,阅读过《论语》的人都会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他的学生变成了弟子,用忠诚和献身与他共同进退,这是相当不同凡响的。孔子向他们讲述他的梦想。孔子梦想这样的一个世界:战争、仇恨和残暴被和平、善良愿望和幸福取而代之。孔子对弟子们一无所求,除了创造条件使这一美梦成真。孔子近乎无情地鞭策弟子们,坚持认为他们只有靠有目的的学习和修身才能成为新型政府中称职的官员。孔子严厉斥责弟子们的懒惰,适时讥刺他们的愚笨,如果他们背离他的原则,他就用藐视来严肃地谴责他们。
孔子弟子的数目被极度夸大了。在《论语》提到的人物中,有22位可能是弟子,后来的《孟子》又增加了两人。不用说,还有一些我们根本不知其名的弟子。一些可能值得相信的传统说法告诉我们,大部分弟子来自鲁国,其他的则来自毗邻的几个国家。 [22] 尽管许多早期的记载在这些方面语焉不详,但还是明确指出,子贡是卫国人, [23] 而司马牛则是宋国的一个主要大家族的后人。
司马牛是孔子弟子中门第最高的人。他的家族在宋国世居高位,他的一位兄长受到宋公的长期宠信。但是,这种优越的政治地位最终却酿成了极大的不幸。尽管不是司马牛的过错,他也未能避免受牵连,最终不得不逃离宋国。逃到齐国后,因为司马牛的贵族地位,齐国给了他一座城作为采邑。 [24] 然而,当孔子接受司马牛为学生时,并没有因为他是贵族出身而对他特别关照。孔子对他很和善,但他的表现不是令人尊敬而是使人怜悯,因为他的思想负担太重,生活并不美满。 [25] 另一方面,孔子心爱的弟子颜回可能是弟子中最贫穷的一位。 [26]
在早期文献中,大部分弟子的家庭背景材料少有记载或根本就没有。乍看上去,至少有将近一半的弟子与《左传》中一些重要的贵族有相同的家氏,但在多半情形中,我们无法知晓他们是不是那些重要人物的近亲。孔子强调他接受所有志向远大的学生,而对他们的唯一要求是聪慧和勤奋。孔子明确宣布,无论贫穷和富有,都不能妨碍一个人才能卓著和奋发有为。 [27] 所以说,一旦进入孔子组织起的这个集群,所有的人就都处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唯一能对他们做出高下区别的只是他们所能取得的成就。
为什么这些学生要投奔孔子呢?首要原因之一当然是孔子的人格魅力,这具有持久的吸引力。毫不夸张地说,即使在《论语》中朦胧反映出的孔子的暗淡而被歪曲了的影像,也穿过了2500年的距离,不断地鼓舞着人们的热情,并激起了许多异域他乡和各种宗教信仰的人们对他的不同程度的崇敬。可以想见,当他在世的时候,孔子肯定被看作是有感召力的“传教士”。作为教师,孔子也对那些有浓厚学术兴趣的人有吸引力。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其他教师能提供进一步研究文学、历史和哲学的机会。尽管人的本性会有变化,但区别并不大,理当具有一些共同的政治追求。所以,我们必须说,孔子能够训练人们从政做官,这是吸引弟子的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实际上,他的训练和他的推荐,确实有助于弟子们取得社会地位。
这并不是说孔子完全利用他的具有实用价值的主张招收学生,一如他的模仿者墨子后来公开进行的那样。 [28] 相反,孔子不断谴责那样的人,他们以原则为借口,而真正关心的却是谋取财富和口体之欲。孔子宣布,假如一个国家治理得很糟,那么,在其中做官的人,只有耻辱而没有什么荣耀可言。 [29] 不过,《论语》也告诉我们,至少有一位弟子以“俸禄作为学习的目标”, [30] 而孔子本人则悲叹“很难找到这样的人,甘心情愿学习三年而不谋想物质报酬”。 [31]
在孔子的首批学生中,只想获得物质报酬的人可能很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他的一些弟子确实得到了很好的工作,有人便抱着精明的实用动机跟随孔子学习了。《论语》提到了22位弟子,其中的司马牛本来就有一处封地。早期典籍只是附带地、多半是偶然地告诉了我们这些人所获得的政治地位。不过,余下的21人中至少有9人成为相当重要的官员,尽管第10位(闵子骞)拒绝了当权者许诺给他的官位。在做官的这9人中,有2人(冉求和子路)的官职是先后在鲁国和卫国获得的。这些职位中最低的也是一座城镇的首长(邑宰),而最高的职位则是有3位孔子弟子相继担任的季氏家宰。 [32] 季氏的家宰是鲁国最重要的位置。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官职是被任命的而不是可以继承的。既然季氏掌握着鲁国的实权,那么,他的家宰就会对国事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尽管一些弟子能够依靠自己的才能得到这样的位置,但那些最重要的职位还是得由孔子设法安排。 [33]
明白了以上事实之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年轻人要去求学于孔子了。但是,那些受到孔子谴责的贵族们却为什么会情愿任用他的学生呢?这看上去可能有些令人惊讶。不过,对于这样的问题:当时的在位者为什么会被这样一种思想——保证其属下是受过严格道德训练的人——所吸引,有一些很好的理由可以解释。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曾指出:“对于自己的行为,专制君主可以设定任意的范围。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他们也可以任意放纵。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根本利益却是让所有的臣民都尊重固有的和法定的社会义务。” [34]
在那样的时代,那些忠实可信的官员受到了特别的重视,成为各国权贵情愿任用的下属。比如说,从西元前505到西元前502年,实际掌握(事实上是恐怖统治)鲁国政府的人叫作阳虎。当时的阳虎,名义上只是季氏的下属——家宰。在接下来的一年,阳虎与其他5人要密谋杀掉“三家”的首领并取而代之。阳虎的阴谋差一点儿得逞,失败之后,他被迫外逃。 [35] 经历了这样的风波之后,即使是那些最放荡不羁的执政的上卿也不得不进行认真挑选,主动任用那些具有可靠道德品质的家臣。尽管孔子倡导要忠于原则而不是个人,但他宣讲的改革是通过说服而不是使用暴力来完成的。在位者完全明白,如果他们把权力交给孔子弟子,就不会导致流血革命。实际上,孔子弟子子路就是在卫国为保卫他的上司而死去的。所以,出现以下情形并非偶然:阳虎夭折了的政变结束后不久,孔子弟子就得到了鲁国政府的职位。
进而言之,孔子传授给学生的是政治原理和治国才能。他们拥有了这些有用的技能,就肯定使他们具有了大大地超乎同代人的长处,因为当时并没有其他人能像孔子那样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机制。弟子们是经过挑选而形成的一个集群,因为孔子不能忍受蠢汉和懒虫。在与他们的夫子和同门的讨论和辩难中,弟子们的才智得到了磨炼和提高。他们的心灵受到历史知识、诗歌和礼仪的陶冶,所以,像子贡这样杰出的孔子弟子,在以鲁国外交官的身份与鲁国政治对手的外交争锋中屡屡获胜就是不足为奇的了。假如季孙去参加与别国的会盟而不带上子贡的话,他肯定会后悔的。 [36] 由于对政治原理的长期研究和对常见政治情势的讨论,弟子们知道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和外交局面。这样一来,当吴国国君出其不意地向叔孙(这个人恰巧瞧不起孔子)索取会盟礼物时,这位大人物张口结舌,无以应对,而正是站在他身后的子贡帮他摆脱了窘境。 [37] 甚至背离师门的子羔(突然中止了在孔门的受教), [38] 也能帮助孟孙拟定外交计划。 [39] 因此,当时的在位者并不是因为喜欢或者是因为相信孔子的政治原则才任用了他的弟子。在位者任用他们,是因为这些弟子有真才实学。
当然,孔子本人的声望对于他的弟子们获得职位也起了一定作用。在这方面,孔子的才智和人格不能被忽视。与他的学问一道,孔子的才智和人格甚至在他有生之年就赢得了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当然,这与中国后来出现的对于他的学术思想的尊崇并不是一回事。然而,在孔子出生前,传统文化已经享誉了几百年,而他则是传统文化最热心的学生。在后来出现的某些儒家传奇中,孔子差不多只是以智者的面目出现,为人们提供所有难题的答案。这是一种夸张,但是我们肯定不能用孔子的出身和社会地位来解释以下事实:他有许多很有地位的故旧之人,他的观点也受到了社会上层的普遍尊重。
【按:前文还说孔子去世时默默无闻,这本书问题挺多的~】
可是,从《论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最成功之处并不是表现在与他同龄人的相处之中,而是表现在与年轻人的交往之中。仔细想来,这并不怎么令人吃惊。作为社会改革者,他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思想,再加上他稍嫌傲慢的性格,使孔子认为自己肩负着一种使命,即抵制当时流行的做人准则,这种情势很容易被青年人接受。孔子并没有像个白胡子老头那样,企图用先知式的知识增强人们对他的信任。事实上,在孔子50岁之前,他的弟子们就在鲁国政坛上施展才干了,这一点确实是意味深长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季氏篡夺了鲁公的权力,并做了许多孔子不赞成的事情。然而,正是季氏才给了孔子弟子们大部分的(如果不是全部的)在鲁国从政的机会。孔子坚持要让弟子们忠实于他们的原则,所以,当弟子冉求执行季氏所制定的征收额外税收的新赋法时,孔子便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弟子。 [40] 但是,孔子并未禁止弟子们在季氏手下做官。要做这样的禁止将会是堂·吉诃德式的迂腐和空想。相反,孔子竭力把季氏人物扭转到他希望他们应该走的方向上去,并且公开而大胆地批评他们。
西元前492年,季康子成为季氏的首领(季孙),他是儒家集群的主要保护人。在当时,季康子是鲁国的实际统治者,除了一些偶然的事件,季康子的政治作为是无所谓善或恶的。季孙的继承人应该是季康子的异母兄弟,但这位兄弟却被神秘地谋杀了,而季康子则被认为与此事有关。 [41] 没有证据证明季康子是凶手,但作为主要受益者,他理当受到怀疑。可是,总的来说处在他那样的政治地位上,季康子的政治行为并不出乎我们的预料。他发动侵略战争,还用行贿的方法防止鲁公的力量变得太大。但另一方面,他也有能力保卫国家。尽管季康子并不喜欢鲁公,却还能客气地对待他。就那时的情形而言,季康子很可能是比鲁公更好的国家管理者。
孔子与季康子的关系是相当有趣的。尽管直到西元前492年季康子才做了季氏首领,但至少在那年的6年前他就开始与孔子来往了。 [42] 除了孔子弟子之外,季康子是《论语》中较多提到的人。他不仅像《论语》中的多数人所做的那样向孔子提问题,而且还参与一些讨论。据此书记载,季康子把一种药送给孔子做礼物,而孔子则做了明智的表态,他说:“我不明白它的药性,不敢吃它。” [43] 几乎对于季康子的每次发问,孔子均以说教和指责的方式作答。有一次,当政的季康子为国内众多的盗贼所困扰,就请孔子给出个主意,孔子告诉他说:“如果你没有过分的欲望,即使有奖赏,也没有人会去偷窃。” [44] 当他请教如何管理国家时,孔子告诉他,最好还是先学会管理自己。 [45]
这些辛辣的回答并未使季康子疏远孔子,而是刚好相反,季康子一定很欣赏这位教师的诚实。他也可能发现,尽管孔子的理想主义的追求不太现实,但却是可敬的。有一次,季康子问孔子,弟子子路、子贡和冉求是否可以做个称职的官员,孔子回答说可以。 [46] 而季康子则最终把这三个人推荐给了他的父亲季桓子。尽管我们没有发现孔子与季桓子面谈的记载,但《左传》告诉我们,季康子掌权的6年前,即西元前498年,子路是季氏宰。 [47] 待到季康子嗣位之后,又任用了一些孔子弟子。
《左传》提到,子路在西元前498年担任着季氏宰,这可能是孔子时代的儒家集群在历史上的第一个可以被信赖的日期。此时,孔子53岁,这证明他已开始赢得了当政者对他的某种程度的政治认可。虽然我们还不能肯定子路担任这个职位有多长时间,但他不可能在西元前502年之前得到这个位置。那一年发生了以阳虎为首的预谋叛乱,而在有关这一事件的详细的史籍记载中并没有提到子路。 [48]
这次预谋也牵涉到季氏的另一位属下。这个人叫公山弗扰,负责把守要塞城邑费地,而费地则是季氏的主要据点(封邑)。公山弗扰对季氏不满,原因不详。可是,他绝对不是像阳虎那样寻衅滋事的暴徒。实际上,公山弗扰并不完全赞成阳虎的所作所为,因为他要捍卫鲁国公室的利益。 [49] 为了确保公山弗扰帮助他实现全盘阴谋,阳虎很可能公开表示过,他背叛季氏的动机是限制“三家”的权力并交还给鲁公。尽管公山可能被导入歧途,但他仍然是个讲原则的人。即使在他不得不最终逃离鲁国时,他仍然用忠诚于国家并反对国家的敌人来证明这一点。这种行为与阳虎截然相反,因为阳虎在出逃之后却竭力怂恿齐国侵犯鲁国。 [50]
阳虎的阴谋失败时,公山弗扰并未马上离开鲁国。相反,公山弗扰占据着费邑,公开背叛他名义上的主人季氏。公山弗扰的立场是反对控制着鲁国政权的季氏,但是,这种局面在当时显然无法长期维持,除非扩大支持他的基础。很可能他梦想着恢复鲁公的权力,将鲁公置于自己而不是季氏的庇护之下。在此关头,他请求孔子参加他的“政府”。 [51]
面对这样的邀请,孔子受到了极大的诱惑。如他所述,他的天职是从政,他的使命是要救世。然而,眼看就是个老人了,如果不马上行动,行将年迈无力的孔子就不会再有机会把他的政治理想尝试着付诸实施了。费地确实是个小地方,而孔子也不赞成暴力革命的原则。但是,季氏流放了上代鲁(昭)公,并以武力世代统治着鲁国。用另一股武力对抗这种不公正,不也是很合乎正义的吗? [52]
对于孔子考虑前往费邑的冲动,子路深感震惊。子路是那种极度诚实的人,这种人坚信“是即是,非即非”。这样的人依靠一些简明的原则行事,并认为轻微的调节或折中都是不道德的。在他的家乡,子路的言行好似一位圆桌骑士。孔子曾教导他说,用武力对抗上司是错误的。那么,在子路看来,因为公山弗扰用武力对抗他的上司,所以,对于公山弗扰就应该像对瘟疫一样地躲避。子路的动机无可非议,尽管它看上去总是有些过度纯洁。同时,我们也要指出,这时的子路可能已经是季氏宰了,所以他有义务消除公山弗扰的威胁。事实上,子路后来真的去履行职责了。
孔子最终打消了加入到公山弗扰行列中的念头,但是,他还是对子路说:“他的确不会是平白无故地召我的。如果有什么人打算任用我,我就不能建立一个新的东周吗?” [53] 换句话说,孔子梦想建立一个新王朝,它将复兴那个已经不幸崩溃了的周帝国曾有过的辉煌。 [54]
除了进行教学,孔子此时还在忙些什么呢?我们只能说一无所知。年轻时他担任过各种非常低级的职务。后来,在生活上他很可能接受了弟子们的接济。孔子接受弟子们的礼物,也可能辅导那些能付钱给他的人。相对来讲,孔子是穷人,也得生活。他很有可能得到了政府的某种生活补助,特别是在引起了季康子的格外注意之后。
传统说法坚持认为,孔子曾在鲁国身居高位,并一度在鲁国的政治事务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左传》的记载是,西元前500年,孔子作为鲁定公的助手(相)参加了与齐国的一次外交会谈(“夹谷之会”)。在那个场合,依靠他的勇气和智慧,孔子挫败了齐国绑架鲁定公的图谋,并迫使齐国退还了已经夺去的鲁国土地。 [55] 这个故事中的许多地方是失实的,一些中国学者很久以来就对这个故事持反对态度。如果这个事件真的发生过,那将是孔子政治实效性的高峰。然而,无论是《论语》还是《孟子》,对此都只字未提。那是一个被加到原典中的颇具传奇色彩的事件,与孔子的一生是不相干的。 [56]
更顽固的一种观点还说,孔子曾经担任鲁国的司寇。乍看上去这似乎是真的,因为三部相对较早的著作,《墨子》、《孟子》和《左传》都断言他曾任此职。可是,仔细考查之后,其中两部书的证明是不能成立的。尽管《墨子》说得相当肯定,但该书中的这一部分被确认是后人附加的。 [57] 《左传》的情形相当奇特,这部书很详细地记载了鲁国历史,并且弥漫着对孔子的强烈兴趣。所以,如果孔子曾是鲁国司寇的话,《左传》应该相当完整地描述他的政治举措。然而,它只在一个地方不经意地提到了孔子曾担任过此职,那是在孔子任职前的西元前509年,文载:“后来孔子做司寇时,他用一道沟把(各位鲁公的)坟墓围合了起来。” [58]
这样的记载是一种消除麻烦的奇特办法。没有人知道孔子任司寇时都做过些什么,只有孟子解释了孔子为什么辞了职。 [59] 后来,当编年史家觉得有责任给他们的读者以孔子一生的完整细节时,便用荒唐的事情填补了这个空白。在他们的笔下,孔子担任司寇时的政绩包括当场处决犯人(少正卯),以及将奇特的罪名,诸如“制作不合常规的衣服” [60] 等,列为受死刑处罚之列。这些事情与我们从较早的和较可靠的材料中了解到的孔子的所作所为都是不相符的。 [61]
孔子做司寇本来就是不可能的。这是个重要官职,正常情况下是由显赫家族的首领担任的。根据记载,在孔子出生的前一年,鲁国公室的亲戚、有权力的臧氏首领(臧武仲)担任着司寇。马伯乐认为,这个职位很可能是世代由臧氏家族继承的保留职位。 [62] 孔子弟子极想让他们的夫子得到世俗政治的认可, [63] 而一旦孔子能成功地得到这样的职位,很难相信《论语》不去记载这个成功的。然而,这本书却从未说过孔子得到过任何政治高位。孟子认定孔子做过司寇的说法仅仅说明在孔子去世的百年之后儒家传奇便开始产生了。 [64]
孔子的几位弟子在鲁国从政后,向来急切从政的孔子却还是未得一职,这肯定会令所有关心孔子的人日益感到为难和不安了。西元前500年后不久,很可能不仅是子路(任季氏宰),而且还有子贡和冉求也为季氏服务。 [65] 在《论语》的记载中,有人对孔子说:“先生,您为什么不从政呢?”孔子回避了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指出,就是做个好公民也是对政府的贡献。 [66] 孔子可能像他的弟子一样,也为自己的政治处境深感窘迫。
然而,如果孔子甘愿不讲任何条件地接受委任,他肯定是能够得到官位的。但这是他不愿意做的。有一次,子贡责备他的老师对从政持超然态度。子贡把孔子的政治才能比作一块美玉,并且说道:“假如我这里有块美玉,我是应该把它保藏在盒子里呢,还是应该找个好价钱卖掉它呢?”“卖掉它,”孔子回答说:“务必卖掉它。你瞧我吧,正等待着好价钱呢!” [67]
孔子想要的价码是,不仅要有权议论政治,还要在政府中有个实权位置,以及得到真正的机会,以便纠正他所谓的现实政治中突出的弊端。执政者当然不愿给他这种权力,这是可以理解的。季康子倒是对孔子的想法很有耐性,甚至还有兴趣,但与此同时,他也一定是心存疑虑地看待孔子这个人的,因为这位哲人不仅有激进的思想,而且完全有能力不遗余力地把他的思想付诸实施。可是,即使孔子成为政府的实际管理者,他又将如何实施其思想呢?当季康子问孔子如何对付盗贼时,孔子回答说,只要季康子克制自己的欲望,一切就会好起来。 [68] 这种说法好似精彩的布道,然而作为对付犯罪风潮的实际对策,这几乎是文不对题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孔子当时的目的不是给出实用性的劝告,但事实上我们并未看出如果他想给这种劝告时就真的能够给得出来。作为他的政治文化的总建筑师,孔子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如果在他的时代让他去负责实际的政治运作,他很可能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69]
不过,尽管不容易说清楚是什么职位或者是在什么时候获得的,孔子最终还是得到了官职。根据有关记载,其时间大概可以确定是西元前502年至前492年之间的某个时候。 [70] 《论语》从未直接告诉我们孔子担任的具体官职,它仅给我们以暗示,像是解谜的线索。孔子显然认为,以他当时的地位,他足以过问任何重要的政治决策。与此同时,还有人坚持认为他根本没有接受过政府的咨询。 [71] 在宫廷里,当他与高级官员(上大夫)谈话时,他是受拘束的和彬彬有礼的,而与下大夫言谈时则是不拘礼节的和非常直率的。 [72] 另外,在《论语》中,孔子曾两次谈到他自己是“跟随在大夫之后的(从大夫之后)”。 [73]
后一个表述是说孔子自己是一位下大夫,他所说的“跟随(从)在大夫之后”是一种惯常的谦逊说法。 [74] 孔子大概不可能是上大夫的同僚,因为他对他们的态度是“受拘束的和彬彬有礼的”。而如果孔子比大夫还低的话,就几乎不可能指望过问国事,因为下大夫在朝堂排序中是最低级的。
我们虽然不知道孔子是怎样逐渐得到这个职位的,但却不难猜出其中的一些缘由。孔子弟子肯定为这项任命出了大力。而且,即使是像季康子这样的人也一定认识到以下情况对孔子是不合适的:孔子本人没有职位,而同时他的弟子们却飞黄腾达。 [75] 中国人总是十分看重所谓的“面子”,所以,很可能是为了顾及各方面的“面子”,当权者才觉得应该给孔子安排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应该是个有影响的头衔,但却没有“重要职责”,也没有实权,以避免让孔子有机会做出一些有碍于在上位者的事情。这样的职位在每个政治机构里都有,目的是转换一些有影响力的个人的能量。因为,这些人如果滞留在政府之外,很可能会给政府制造麻烦。我们应该记得,孔子曾与公山弗扰反对季氏之叛乱的行为有瓜葛,这可能会促使那些大人物们相信,像孔子这样的知名人士,如果长期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迟早会给政府造成不便。于是,他们给了孔子一个头衔,这个头衔相当于国家的咨政(顾问)之类。
我们的考证几乎可以确定,孔子的职位终究是个闲职。很自然,这使后儒颇惑困窘。在他们看来,孔子理所应当是当时最重要的人物,比如鲁公的首席谋士。 [76] 可是,事实上《论语》只记录了孔子与鲁定公的两次会谈。以此看来,孔子的职位可能是鲁定公任命的。 [77] 在这两次会谈中,鲁定公所问的问题仅仅是向一位智者求教,而并不是我们预料之中的君臣间应有的交流。 [78]
一些儒生严重曲解了孟子所说的孔子从政的事实。孟子说,孔子并不是在鲁公手下,而是在季氏当时的首领季桓子手下做事。 [79] 后来的儒生们不相信孔子会屈尊就下服务于像季桓子这样的篡权者。可是,孔子的职位实际上只可能在名义上属于鲁公。既然鲁公是“三家”或季氏的傀儡,孟子就只好采取一种实实在在的说法。所以,最大的可能性正是孔子的朋友季康子(季桓子之子)给孔子实际安排了这个位置。 [80]
孔子接受的这个职位事实上仅仅是用来让他保持政治缄默的,但这种缄默明显有损于孔子的正直。的确,保持政治缄默与孔子反复声明的主张是不一致的,这个主张就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讲求廉耻的人,只有在他能够有效地为一个良好政府做贡献时才可以接受官俸。但是孔子真心希望自己无论如何都要获得这样一个机会。孟子说,孔子“在季桓子手下做事,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有被付诸实施的可能性(“见行可之仕”)”。一些弟子无疑也劝说孔子接受一个职位,以便测试这种可能性。他很可能情愿去做,这主要是因为年岁的缘故。既然孔子已经50岁左右了,他就不能再期望获得更好的机会和无限的未来了。
鲁国几十年来与他国的和平相处时常被断断续续的国内叛乱所扰害,这些叛乱总是以“三家”的某个封邑为中心。当初,这三个大家族把这些地方建成了坚固的要塞。但是,在控制了鲁国之后,他们迁居到了首都,并留下邑宰把守他们的封邑。对于那些具有叛逆之心的邑宰来说,占据这样的要塞显然是一种不断的诱惑,从而致使他们一次接一次地发动叛乱。西元前498年,担任季氏宰的子路建议拆毁“三家”的要塞,以便消弭这种危险。 [81] 这一计划马上被“三家”的首领所接受,并在初始阶段进展顺利。可是,不久之后就出现了军事对抗, [82] 使这一计划在其最后阶段未能进行到底。
这个计划的失败可能是子路失宠于季氏的开端。实际上,在此之前,子路已经在政治上大获成功了。孔子已经是够不妥协的了,但是也很难看到子路会一直追随季氏,因为与那些最坚定的极端道德拘谨者一样,子路的政治信条也是百折不挠的。他不会无限期地追随季氏。《论语》记载,另一位朝臣向季孙讲了子路的坏话,这使季孙开始不信任子路了。 [83] 子路的影响力可能在下降,而与此同时,冉求的影响力却在上升。 [84] 尽管冉求也是孔子弟子,但他在政务上并不受孔子之教的牵制。冉求“懂得把黄油抹在面包的哪一面”。 [85] 我们不知道子路继续供职于季氏有多长时间,但在孔子开始周游列国之前,子路就很可能因招人嫉恨而被免职或辞职了。
从《论语·子路十三》一章中可以看出,有了职位的孔子并不快活。这一章记载的是,有一天,冉求从宫廷归来时,孔子问他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冉求回答说,有一些国家政务需要处理。孔子一听这话就生气了,他说:“那些一定是低级事务。 [86] 即便他们没有让我担负真正的责任,但是,如果有什么可称之为‘国家政务’的重要事情的话,还是一定会来咨询我的。” [87] 然而,不久之后,孔子就连这种幻想也放弃了,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在此时的鲁国,他已无指望能做成任何事情。孟子认为,正是因为“不被任用”,孔子才作出了离开鲁国的决定。 [88] 虽然他几近60岁,还是踏上了周游列国的旅程,决心去找寻这样的一个诸侯:给予他真正的机会,把他的大道付诸实施。 [89]
对于孔子周游列国的旅程,我们只有一些零碎而不连贯的资料。写成于汉代的《史记·孔子世家》倒是有一个详尽而复杂的旅程表,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后来的东西作为向导,因为它的许多地方明显是杜撰出来的。根据《论语》、《孟子》和《左传》的记载,我们有可能列出一个清单,说明他都访问过哪些国家,也还可以根据这些资料的记述,制作出另一个旅程表,甚至道家著作《庄子》也能作为这方面的佐证。 [90]
在孔子周游过的地方中,只有一部分是难以确定的。《孟子》说他访问过齐国,《论语》和《墨子》说他见过齐景公。 [91] 可是,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孔子在他后来的这次周游中造访过齐国,而且我们也怀疑他能否做得到,因为齐景公死于西元前490年。 [92] 所以,可能如《史记》所言,齐国之行发生在以前的某个时候。后来,一些对于儒家传统进行了详细考证的人讲述了一些孔子到访齐国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很显然是靠不住的。 [93]
那么,孔子是何时离开鲁国开始这次长期周游呢?这仍然是个在无休止地争论着的难题。《史记·孔子世家》提供的是自由选择,在不同的篇章给出的时间分别是西元前498年、西元前497年和西元前496年。 [94] 不过,无论如何这个时间不会晚于西元前493年,因为孔子在卫国见到过的卫灵公就死于这一年。 [95]
随行孔子出游的弟子是谁,以及每位弟子与孔子相伴多长时间?这是另一个不可能得到答案的难题。根据传统说法,孔子有大批的随行者,但是,这种说法很可能是受到了后代游仕之士大规模活动的影响。约100年后,孟子周游列国时,据说是“随行的有数十辆车,几百人”。 [96] 后人可能觉得,以孔子的尊严,至少得拥有堪与孟子相比的随行人员才能说得过去,但这显然只能以轶事作根据。不用说,传统说法夸大了孔子随行者的数目。 [97] 事实上,能被确证随行孔子在国外的只有两位弟子,那就是子路和颜回。 [98]
孔子先到了卫国。孟子说,子路之妻的姐夫(弥子瑕)受宠于卫公。这位贵族告诉子路说,如果孔子能住在他家,就能成为卫国的高级官员。孔子拒绝了这一要求。 [99] 不过,孔子仍然得到了卫公的礼遇,而孟子说孔子还在卫国从政了。可是,这种说法除了是说卫君待孔子以国宾并从国库里给他一些津贴而外,可能再没有其他意义了。正如孟子所示,孔子很可能得到过好几个国家类似的资助。 [100] 因为孔子并不富有,如果没有资助,孔子一行便不能周游下去。但是,如果因为孔子得到了资助就说他担任了某国的官职,却是不符合实情的断言。既然孔子弟子希望孔子去做官,并认为这个世界在漠视他,那么,假如孔子在周游列国中真的得到过任何实在的政治地位的话,《论语》是会道出这一事实的,但事实上《论语》从未陈述过此类说法。 [101]
卫灵公之妻是著名的南子,她被认为是个声名狼藉的女子。史书的记载指责说,她与其兄有乱伦关系,并在她婚后还继续着这种不正当的勾当。她也涉足于政治阴谋。 [102] 《论语·雍也第六》“子见南子”章说孔子会见了南子。这可能是她的命令,但子路认为这种会见有悖于孔子素日所为。后世的儒生认为这项记载的确太有损于圣人的形象,以至于一些人希望从《论语》中删去这种诽谤性的章节。
孔子发现,卫国的情势有似于他已离开的鲁国。他受到尊敬和资助,但却没有机会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103] 我们不知他在卫国待了多久,只知道他是在西元前492年之前离开的。 [104]
孔子往南去了陈国。 [105] 他经过宋国时,该国的一个名叫司马桓魋的显贵,企图伏击并暗杀孔子。 [106] 没有原因可以解释这次企图,甚至《史记·孔子世家》也没说什么。可是,也有一些相关的证据,再加上纯粹是根据当时情形的推测,我们即使不能说明其真实的动机,却还是提供了一个可以表面上说得过去的理由。但是,要想讲出这个理由,我们还得离题一点。
司马桓魋是宋国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家族的一员,是最恶劣的巧取豪夺的贵族。他是宋景公的幸臣,并利用这一地位去强夺他看中的别人的财产。可是,每当这类事情使他严重受挫时,他既无勇气防御,又无勇气报复。尽管由于他的傲慢而使其他几位重臣与宋景公疏远,甚至还导致了一些人的叛乱,他还是被宠幸着。直到西元前484年,他才开始失宠。西元前481年,宋景公要杀他,桓魋与家族中的所有其他成员不得不逃离宋国。 [107]
司马桓魋的弟弟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但是司马牛是何时从学孔子,从学多久,我们并没有看到相关资料的明确说明。根据一些不太可靠的记载,司马牛可能是在孔子离开鲁国之前的某个时候成为其弟子的。 [108] 不过,虽然司马牛成了孔子弟子,但也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他因从学孔子而反对他的兄长司马桓魋。可是,对于像他兄长那样的“君子”,司马牛显然不会有太高的评价。在举家逃离宋国之后,司马牛拒绝与司马桓魋同居一国。 [109] 更有甚者,司马牛有一次竟悲叹自己“没有兄弟”, [110] 而事实上,司马桓魋和他的另一个兄弟仍然在世。 [111]
作为孔子弟子,司马牛肯定懂得轻视这样的人,他们自认为凭着贵族出身就使他们有资格堕落下去。相反,正如同门子夏告诉司马牛的,儒者相信,真正的君子会以尊敬和礼貌对待所有的人。这样一来,周围的人,全世界的人,就都会是自己的兄弟。 [112] 孔子教导司马牛说(正如后儒最终教导全中国人一样),一个人之所以高贵,依据的是心灵和精神,而不是血统。某个人之所以值得依靠,也并非因为他祖上是什么人。然而这个新的价值结构与司马牛亲属的行为格格不入,这使他忍不住要有一种不祥之感和焦虑意识。为此,孔子告诉他说:“如果反观内心时,你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什么错误,你就不会有什么忧虑和恐惧了。” [113]
然而,在司马桓魋看来,孔子所倡导的东西显然正是苏格拉底(Socrates)被判的罪行:腐蚀青年。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才企图暗杀孔子。可是,应该强调的是,我们不能断定这就是他之所怨,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司马牛就学于孔子的日期。
无论如何,孔子是以坚强的意志行事的。他自称受命于上天,而司马桓魋则无权干涉天命。孟子说,孔子在经过宋国之前就已穿上了“不引人注目的衣服”,以便预防不测。 [114] 《论语》也记载了孔子一行人在匡地经历过的一次非常相似的险情,这可能是同一事件的另一种记述。在匡地的那次险情中,颜回与众人跑散了,孔子担心他被杀,但最终他们又团聚了。 [115]
孔子和他同伴的这些受窘事件很可能发生在去陈国的路上。事实上,据说他们曾因缺乏食物而变得很虚弱。 [116] 可是,他们最终到达了陈国的都城,在那里,孔子被一位大臣当成公室成员一样的贵宾来接待。 [117]
《左传》说孔子于西元前492年在陈国,此时,这个不幸的国家已经走上穷途末路。像它的西邻小国蔡国一样,陈国的南部已被强大的楚国视为自己的疆域。这两个小国变成了两个“蛮夷”之国——楚国和吴国——相互争斗的走卒。楚国在西元前494年占领了蔡国,并命令它的人民迁出国土,以报复它附从吴国。陈国有一次拒绝帮助吴国进攻吃了败仗的楚国, [118] 但这种保持中立的企图是徒劳的。陈国时常遭受侵略,入侵者先是吴国,后是楚国。到了孔子访问后的第12年,楚国终于灭了陈国,吞并了其领土。
在一次侵略战争发生时,孔子可能仍在陈国(鲁哀公六年,西元前489年)。总之,陈国君主难得有闲暇讨论哲学,他一定也很难被说服去相信德行能导致和平、繁荣和幸福。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孔子曾会见过陈公。根据记载,孔子只谒见过陈国的司败(司寇),而这位显贵对孔子也并没有多少好感。 [119] 孔子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朋友, [120] 他开始思念家乡鲁国。孔子明确讲述了归国之意,并认为因为身在异域,便约束不住一直留在鲁国的弟子。 [121] 不过,尽管有上述种种令人沮丧的情形,孔子却并没有停止过他的政治求索。
这一时期,只有一件事情是真正有趣的,那就是两位著名人物的会见。一位是孔子,另一位是楚国知名的贵族叶公。可是,有一个问题必须要澄清,那就是,在楚国君主自称为“王”,“公”只是国内某一区域的统治者。 [122] 不过,叶公是个有权力的人,据说是楚国君主的亲戚。在这个国家,叶公不仅是个有权力的人,还是个不同寻常的讲求原则的正派人。叶公一度是楚国左军的统帅,指挥过无数的军事行动。在一些场合,《左传》把他描述为像孔子那样的有主见的人。叶公坚持道德而不是武力的重要性,倡导宽待人民,还批评那些明目张胆地损害国家利益的贵族刺客。《左传》中诸如此类的言论并不总是可信的。有时我们发现,它们出自那些行不践言的人们之口。 [123] 可是,叶公却是言行一致的。据说他在民间声誉很好。在与孔子会见后很久,一个叛乱者谋杀了控制国家政治的楚国令尹(宰相)之后,叶公率领军队平息了这场叛乱。同时,由他管理的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恢复了秩序。这些都做好之后,他让前令尹的儿子继续担任令尹,自己则返回叶地。 [124]
孔子自然想会见这样的人,而叶公想必也对孔子的思想感兴趣。大抵叶公此时正在楚国的邻邦小国蔡国,巩固楚国对它的吞并。孔子可能是到蔡国会见了叶公。 [125]
我们只有他们会谈的只言片语。叶公问孔子应该如何治理国家,孔子的回答是,一个真正良好的政府要关心它的臣民,以至于不仅让他们感到愉悦,还要让别国之民也希望受其管辖。 [126] 假如我们相信《左传》,孔子的这种说法与叶公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也讨论了伦理问题,即一个人是先忠于家庭还是国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任何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所长期争论的难题。叶公主张先国家,孔子主张先家庭,而两位可敬的君子最终接受了这种不一致。 [127] 确实,叶公拿这位流浪哲学家和自命的政治家没法子。叶公问子路,他的老师是哪种类型的人,子路不知如何作答。子路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他是这样一种人:那么倾心于启发那些渴望知识的人,以至于忘记了吃饭;那么陶醉于他的所作所为,以至于忘掉了忧愁;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他的老年已经悄然而至了。’” [128]
孔子日渐衰老,但他并没有中止他的政治求索,也没有返回鲁国。很可能就在此时,孔子又一次受到了他最想得到的东西——官职——的诱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又是个复杂的问题。这次的邀请来自晋国的一个城邑。晋国曾一度控制了大半个中原地区,但眼下却被内战所分裂。战斗的双方是这个国家的两个大家族,而晋公则成了他们的傀儡。总的情势扑朔迷离,但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先是一个家族,后来又是另一个家族,当他们控制了晋公之后,就以晋公的名义颁布命令。 [129] 其中一个家族中的一个下级官员(佛肸)控制了一座城邑(中牟),邀请孔子来加入。与上次对待公山弗扰的邀请一样,孔子倾向于动身而去。可是,就在此时,另一个家族控制了晋公,这个下级官员便策略性地发动了叛乱。 [130]
在此类问题上一向明察秋毫的子路马上指出了这一点,坚持认为孔子不该与叛乱者联合,因为这样做一定会败坏自己的名声,损害自己的原则,而孔子对此的答复则标志着他长期周游求仕的悲怆经历已经臻致顶点。孔子说:“有时,你说的可能没错。但是,不也有这种说法吗?有些东西‘是那样的坚硬以至于不能被磨损’,并且‘又是那样的洁白而不能被染色’。我难道是个瓢葫芦吗?只能悬挂在那里而不能食用吗?” [131] 孔子正在变得实在不能容忍这个世界了,因为对于他的政治追求,这个世界表现出了出奇的冷漠。可是,到了最后孔子还是没有去晋国。 [132]
这场经历颇为类似于前文描述过的事件,即《论语·阳货十七》中提到的公山弗扰对孔子的邀请。只是在这两个关头,《论语》才认为有人给孔子提供了一个政治实权的职位。但是,在这两次事件中,提供职位者都是仅仅控制着小城邑的下级官员,而对于每一次的邀请,孔子都强烈地倾向于接受。这个事实说明,孔子是如何地不被他的时代所认可,并证明了后来说他当上高官的那些故事的荒谬性。毫不奇怪,一些儒家学者珍惜他们的孔子的尊严,认为有义务证明《论语》这些章节的虚构性,并且有时重复了一些非常可疑的主张来实现这一目的。 [133]
我们不知道孔子在陈国待了多久,有关这几年的情况我们只知其大概,而且比通常的材料更少。当我们在西元前484年再次得知孔子的行踪时,他又返回了卫国。
此时的卫国正处在最不幸的状况中,这个国家正由一伙针锋相对(有时是兵戎相向)的君主和大臣把持着。即使在那样的一个恣意妄为的年代里,这些君臣中的一些人的表现也是令人瞠目的。我们说过,国君(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被指责有乱伦行为,所以,她是那样的声名狼藉,以至于仅仅因为孔子会见了她一次就使子路大为烦恼。南子的儿子蒯聩是合法的继承人(大子),据说他因为羞于母亲(继母)之所为,就策划杀掉她。且不论在此情形下弑母是否正当,但无论如何大子的行为也并不是可钦可佩的。他不是亲自动手,而是命令一个家臣去干,但此人在最后一刻精神崩溃,未能下手。南子看出了杀气,啼呼着奔向卫灵公。尽管大子把弑母的行动归罪于这个家臣,但是他和他的追随者还是不得不逃离卫国。 [134] 结果是,当卫灵公在西元前493年死后,大子蒯聩逃亡到晋国,他的儿子(辄)继承了君位,这就是卫出公。而在晋国,几个大家族正在相互争斗,其中一个贵族世家(赵氏)支持蒯聩返国继位,就用武力帮他占据了卫国的一座邑城。 [135]
这样,当孔子再次访问卫国时,卫国的情形是,儿子(卫出公)在都城的宫殿之内做国君,父亲则以武力据守着一座边远城邑,伺机夺取君位,形成父子争国的局面。而在国中,实权并未掌握在卫出公那里,而是掌握在一个叫作孔圉(孔文子)的大臣手中。 [136]
孟子后来说,孔子此次在卫国时得到了卫出公提供的经济资助, [137] 但没有证据说明孔子曾拜见过卫出公,这可能是因为卫出公年龄太小了。 [138] 可是,孔子受到了孔文子(孔圉)的尊敬和遵从(孔文子尽管与孔子同姓,但没有根据证明他们之间有亲属关系)。
我们对孔文子知之甚少,但却有足够的理由证明他绝非圣贤。为此,一些中国学者颇为孔子与他交往的事实所困扰。可是,他们在此却误解了孔子。孔子希望只与那些跟他的行动和理想相一致的人来往,他当然也非常盼望这样的人能够占据有权力的位置。但事实上他们与孔子一样,也得不到实权。这样一来,既然孔子希望影响政治的实际运作,他就得做出选择,只好与那些还达不到他的标准的人来往,并努力调节他们的行为。这并非意味着孔子最终放弃了原则,不加区别地与人交往,而是他遵循了常识,采用了常规的为人之道。孔子的弟子们(像孩子指责家长的行为一样)期望他坚定不移地遵守原则。对此,在某个场合,孔子告诉弟子们:“当我与人交谈时,我不应该对他们可能犯过的错误负责,为什么要对人家那么苛刻呢?……我不能因此而对他们过去的行为负责。” [139]
在此时的卫国,我们不能确定孔子是真的得到了官位呢,还是仅仅作了孔文子的重要宾客。可是,我们很清楚孔子为什么要待在那里。此时,孔文子是卫国的实际统治者,孔子要想影响政府的行为,一定得通过他。而且,孔文子也在寻求孔子的指点,有些场合甚至是依之而行。总的来说,他可能只是一个胆大妄为的当政者。最后,无论他有什么样的短处,孔文子的确是个诚恳的知识追求者。孔子说他是:“勤奋而好学,不羞于向比他地位低的人请教。” [140]
尽管他有长处,孔子对他的一些出格行为也有一定的耐性,但是孔文子对这种耐性的试验却有些过分。孔文子娶了卫灵公的女儿,并认为这么高的联姻可以巩固他的权力,以至于强迫卫国的另一位贵族(大叔疾)与其妻妾分手,转而迎娶孔文子的一个女儿。当这个贵族继续与前妾寻欢时,孔文子就想带兵去攻击他,并问孔子怎么去做。孔子憎恶整个事情,告诉孔文子取消这个计划。虽然孔文子照孔子的劝告做了,但孔子还是命令弟子们准备马车,意思是要离开卫国。 [141] 于是,孔文子立刻向孔子道歉,而孔子也打算重新考虑。但在此节骨眼儿上,鲁国派来了使者,邀请孔子返回家乡。 [142]
孔子虽然不在鲁国,可是一些留在鲁国的孔子弟子却很忙碌。早在西元前495年,子贡就出席了一次外交盟会。西元前488年,在举行另一次盟会时,吴国的一位权臣召唤季康子(鲁国的实际统治者)出席,季康子不敢去,就让子贡代替。在此次盟会上,子贡以一番雄辩化解了麻烦,没有因为季康子托故不来而在当时跟吴国闹翻。此后,子贡不断地表现出自己的外交才能,证明了自己在鲁国政坛上是有用武之地的。 [143]
直到西元前484年,我们才看到有关冉求政治事业的消息,但那时他已经得到季氏宰这个发号施令的位置了。那一年,齐国的一支军队入侵鲁国,冉求筹划了抵御方略,并促使三家的首脑加入行动。冉求自己率领“左军”,樊迟(后来也成为孔子弟子)做他的副手。在这一仗中,参战的一支鲁国军队(右军)被击溃,但冉求却很有效地指挥了他属下的军队,致使侵略者不得不撤退。 [144]
也正是在同一年,孔子接受了鲁国当政者的邀请,回到了鲁国。很可能是冉求获得的威望促成了此事。他们年迈的老师为了实现自己所追求的某种东西,到现在已在外面流浪了十多年,留在鲁国的弟子一定非常希望他回来。他们确实对他感情深厚,而孔子在周游中的遭遇对他们心灵的平静或对他们的作为门徒的自尊也没有什么益处。《左传》告诉我们,“鲁国的使者带着礼物来卫国请他回去”。 [145] 通常是请某人担任官职时才送上这样的礼物,可能孔子是被邀恢复他(几乎是了无意义)的原职。这时,孔子并没有幻想鲁国的当政者会给他实权,但是他毕竟对其他所有地方也都失望了。孔子当时是67岁,而在鲁国至少还有他的朋友和弟子在等着他。于是,孔子回去了。
有一种说法是,把孔子(表面上一事无成)周游列国比作那位枪挑风车的受人欢迎的拉曼查(La Mancha)骑士的四处周游。但是,如果加以认真思考,其间却有根本的不同。堂·吉诃德(Don Quixote)是过去的回声,他模仿的是奄奄一息的游侠骑士的冒险周游。孔子是未来的先知,他的哲学旅程虽然看上去无所成就,但却变成了接下去的几个世纪的思想和政治模式。堂·吉诃德依仗着滑稽的骑士精神的周游,敲响了他所倾心的骑士时代的丧钟;而孔子则通过在他的流浪中竭力寻求将他的学说付诸实施,保证了后来踏着他的足迹前进的周游者们彻底摧毁了他所憎恶的暴虐的世袭贵族制(世卿世禄)。
尽管说孔子周游列国没有取得外在的成就,然而,如果他一直待在鲁国,他就会真的成为另外一个人。不错,适合他的地方是思想的王国,并把这些思想教授给他人。也就是说,孔子不具备那种为把他的思想付诸实施所必需的政治妥协的才能。但是,孔子始终在努力进行着不懈的尝试,这才是最重要的。这种不同就是以下的区别:指挥官说:“跟我上!”追随他的人说:“前进!”如果孔子待在鲁国,陶醉于一个闲职,满足于与学生漫游,那么他将只是一个布道者。而顺着他的无望的探索走下去,他却变成了一位先知。这位可敬君子的这幅图画(在某些方面仍不很完满),始于他的50多岁。他要救助世界,说服他那个时代的顽固的统治者不要压迫他们的臣民。这种行为在一些方面显得有些荒诞不经,但那是只有伟人才会具有的意义深远的荒诞不经。
孔子被邀回鲁的事实不能被理解为季氏家族中的部分人或其首领季康子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孔子简直无法平静下来,因为这个穷奢极欲的贵族策划了一个增加其收入的计划,根据孟子所说,是要将税收提高两倍,而被征税的对象自然是他的饱受贫困之苦的臣民。《左传》说,季康子派家宰冉求去征求孔子对此计划的意见。很难理解季康子的此一举动,除非是他希望依靠孔子对此计划的承认来申斥公众对这个新的征税措施的反对,因为孔子是众所周知的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季康子可能会这么想:几年来他供给孔子以俸禄,此时正是他从孔子那里得到一些报偿的时候。可是,他得到的却是孔子的谴责。 [146]
可想而知,孔子的谴责不可能阻止这个计划的实施。季康子强力推行了新的税制,而冉求作为季氏的家宰,可以说是在为季康子聚敛财富。这就产生了早已露头的首要问题:冉求是季氏的人呢,还是孔子的人?孔子希望他的弟子们忠于他们的上司,但是孔子认为,弟子们的最高义务是服从原则。如果因为要忠实于原则而不能听从上司的命令时,他们的义务就是辞职。 [147] 可是,冉求不是那种为一些小小的顾忌就抛弃远大前程的人。以前,冉求也曾迟迟疑疑地干他的事业,但是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就使孔子忍无可忍了。孔子告诉弟子们:“他不是我的门徒。我的孩子们,敲着鼓去攻击他。我允许你们去这么做。” [148]
这是记载下来的唯一的例子——孔子明确地驱逐一位弟子,但是这种逐斥显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冉求仍旧是儒家集群中的一员,他是否真的被责罚,我们不能得知。 [149]
对于孔子暮年的活动,我们知之甚少。在周游列国期间,孔子无疑收集到了某些历史典籍的原稿和资料,并且可能花了一些时间整理它们。孔子有可能重新确定了一部诗歌集中的某些篇章的次序,这部诗集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诗经》。 [150] 毫无疑问,孔子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教学上,并且很可能就在这一时期招收了大批学生。通过从政弟子,孔子对鲁国的政治事务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当卫出公不得不逃亡到鲁国时,冉求和子贡来见孔子,商议如何对待这位国君。 [151] 孔子还保持着礼节性的社交关系,至少与季孙是如此。 [152] 然而,对于孔子力图以个人身份介入政府决策行为的事情,我们只知道一例,这就是在齐简公被谋杀的事件上。
早在两个多世纪之前,陈国君主的一个儿子从陈国逃到了齐国。齐国君主友好地收留了他,还让他担任齐国的官职,而他则在齐国建立起了众所周知的以他的祖国命名的陈氏家族。陈家在齐国不断发展壮大,并且连续几代都出现了有才能、有性格的后继者。可是,这个家族起先在齐国并不处在发号施令的地位。《左传》记载,在孔子尚处年少的时代,陈氏家族就依靠向人民的慷慨施舍而得到了公众的好感,这个家族的成员也开始涉足一些政治阴谋。他们利用欺诈、背信和暴力等手段清除掉了一个又一个妨碍他们控制齐国政治的更有势力的家族。西元前489年,陈氏家族深深地卷入对一位齐公(他还是个孩子)进行谋杀的事件中,取而代之的是陈氏扶立的齐悼公。因为齐悼公并没有陈氏所希望的那样驯服,于是4年之后齐悼公也被神秘地谋杀了(史书上没有说出凶手)。齐悼公的儿子是齐简公。齐简公的支持者计划把陈氏驱逐出齐国。但在西元前481年,陈氏抢先发动叛乱,杀死了齐简公。 [153]
在此关头,孔子提议要对齐国政治加以干涉。齐国是鲁国的北邻大国,许多年来,鲁国一直保持着较小国家的屈从状态,并不断与齐国发生战争。由于齐国被粗暴和肆无忌惮的陈氏家族所控制,所以孔子认为陈氏既得不到齐国人民的支持,也得不到鲁国的帮助。
孔子听到陈氏家族发动叛乱并谋杀了齐简公的消息后,先是沐浴更衣(以与提出庄重的建议相称),然后去晋见鲁哀公,建议讨伐齐国。鲁哀公说:“鲁国被齐国弄得衰弱不堪已经很久了。如果我们企图进行这样的讨伐,会有什么收获呢?”孔子答道:“陈恒(陈氏的首领)谋杀了他们的君主,齐国有一半的人民会反对他。如果再加上鲁国的军队,我们就能获胜。”鲁哀公接着说:“把这个提议告知‘三家’吧。”孔子果然去通告了,但“三家”不愿意采取行动。 [154]
死亡的钟声在孔门响起了。孔子的儿子孔鲤(缺乏突出的才能,也使孔子很失望)在孔子晚年去世。 [155] 一个更沉重的打击是他的心爱弟子颜回的亡故。 [156] 西元前481年,社会地位最高的弟子司马牛也死于悲惨境地。 [157] 西元前480年,人们看到了勇猛无畏的子路的结局。在卫国的一次叛乱中,子路死于全力营救他的主人。如孔子所预言,子路恰恰是死于非命的。 [158]
这些损失一定被全部告知孔子了。回顾自己的一生,孔子肯定认为他的收获甚微。在改进鲁国政治现状方面他几乎无所建树,他也从未如他所愿地取得控制一国的成就。他最好的弟子去世了,在世的弟子并没有异乎寻常的前程。他既无望他的诸多思想观念能被实实在在地传给后人,也无望这些思想在现实中能得到有力的推进。没有人怀疑孔子对子贡所说的:“哎嘿,没有人能理解我呀!” [159]
然而,除了这些罕见的沮丧之外,孔子没有别的什么抱怨,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曾沉溺于那种最廉价的和最普遍的享受——自怜之中。对于他这样有抱负和洞识的人来讲,失败当然是一剂苦药,但是他所缺乏的只是些外在的东西,诽谤是附加的一种考验。《论语》说,有权势的叔氏不断地诽谤孔子; [160] 孟子则说,孔子“受到众多小人的骚扰”。 [161] 在当时,历史的斯芬克斯之谜并未显示出,总有一天,他那个时代的所有傲慢的统治者的名字会被忘掉,而孔子的名字却会被传颂到世界末日。当然,那时的孔子无此梦想,但他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悲哀。
孔子逝世时的情形并没有可信的记载, [162] 可我们知道他是如何面对死亡的。根据记载,孔子多次得过几乎致命的疾病。在其中一次的病重期间,善意的子路悲叹孔子从未做过高官,就让弟子们装扮一番,如同家臣照料一位达官显贵一样。当孔子再次清醒过来并看到了给他上演的这场闹剧时,他便斥责子路说:“我没有家臣,你们却找借口做家臣,你们想让我欺骗谁呢?我将欺骗上天吗?而且,我死在像你们这样的朋友手中,难道比死在家臣手中更糟吗?” [163]
另外有一次,子路要求孔子允许为他向神灵祈祷,孔子问道:“有这回事吗?”子路向他保证这是习俗,但孔子只是笑笑说:“这样的祈祷我已经做了好久了。” [164]
孔子死于西元前479年。孟子明言,弟子们在孔子墓旁守丧三年,而子贡又多待了三年。 [165] 尽管孟子没有详述三年守丧的是哪些弟子,但从上下文来看,他可能是指当时在门下的所有重要弟子。乍听起来,这好像是被后代人附加在孔子传记中的一个“奇迹”。在西方人看来,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这些弟子中,有的很年轻,有的正值壮年,有的事业刚有开端,还有一些人的事业正在高峰,他们要花掉生命中三年的时间,几乎无所事事地服侍于孔子墓地。这实际上将是“活着的祭品”。为了谁呢?不是双亲,不是君主,甚至不是一个世俗身份很高的人,而只是为了一个卓尔独行之人——他从未升至高位,也没有多少实际的政治成就,那只是他们多年来的老师。
那么说,我们能相信这样的故事吗?这时候,我们记起了这样的事实:《左传》记载,在孔子死后,孔子弟子突然烟消云散了好多年。(只有意味深长的例外,即脱离孔门的弟子子羔还时常出现) [166] 我们看到了弟子们如何崇敬孔子,以至于子贡把孔子比作日月。 [167] 而有若则说:“自从人类出现到现在,从未有过可以与夫子相提并论的人。” [168] 在我们考虑能否相信他们的时候,可以被称作奇迹的这些事件毕竟发生了。而我们也能理解,这位简朴的教师在后来是怎样逐渐成为众所周知的“无冕之王(素王)”的了。
第五章 人
孔子是哪种类型的人?他喜欢接触的、与之交谈的、想去了解的又是些什么人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当然不能仅仅依靠他的弟子和朋友提供的证明,我们也应该考虑孔子政治和思想的对手以及(甚至更好的是)那些想对他保持中立态度的人们的看法。可是,从后几种被认为是相对可靠的人们那里,我们几乎一无所得。在本书的后文,我们将考虑敌对哲学家中党派观念很强的那些人对孔子的攻击,但我们会发现这些攻击几无可取之处,因为此类攻击的内容与曾经在世的真孔子没有关系。确切来讲,这些敌手们批评的对象是有权势的头面人物和被人痛恨的政治集团,他们把他们认为的最有损于人的无论什么性质的东西,都堆在了孔子的头上。一般来说,从这些攻击的细节来看,它们的内容立刻就会被认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再次把我们研究的主要根据——《论语》作为可以利用的最可靠的材料。 [169]
即使是孔子对手的攻击也很少与我们得之于《论语》的一种印象相矛盾,这种印象就是,孔子是个快乐的人。这本书告诉我们,“闲暇之时,夫子的举止是不拘礼节的和愉悦的”。在另一个地方又说他是“和蔼而又严肃,威风凛凛而又不甚刻板,威严而又快乐”。 [170] 孔子的确是令人尊敬的,我们可以毫无奉承地说,他的受人尊敬是理所当然的。反过来讲,孔子也希望得到他人应有的尊敬,并认为他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地位。 [171] 然而,对于他的同胞,即使是社会地位低下之人,孔子也完全没有高高在上的表现。孔子不仅宣讲,而且也实践着他的民主作风。 [172]
我们不相信孔子会是那种人,即总是一个庞大的和热情洋溢的由相识者组成的集群的中心。孔子有许多忠实可靠的朋友,但他不是贪图虚名的人。孔子太有思想,也太坦率了。他说:“把怨恨隐藏起来,表面上却对人家装作友好。……我对这种行为感到耻辱。” [173] 孔子多半是采取以下做法:当面批评,背后表扬。 [174] 这为的是赢得尊敬而不是名望。总的来说,孔子是有某种保留的。这种保留甚至扩展到对他儿子伯鱼的态度上。孔子坦率地承认,伯鱼的才能是令他失望的。 [175]
由于孔子总是以礼貌待人,所以被认为有曲身阿贵之嫌。可是,当他与国君或有势力的世袭贵族谈话时,从未有过任何逢迎巴结的举动,而通常是提出相当严厉的批评。这方面的实际智慧是可以商榷的,但却与他的坦诚相见的观念相一致。部分是由于同样的态度,孔子不喜欢辩才,也不信任多嘴多舌、喋喋不休的人。如果我们根据《论语》做出判断的话,孔子自己从不这样做。孟子引述孔子的话说:“我没有演说的才能。” [176] 尽管孔子的言语有时既动人又高雅,但却很少是啰唆不止的或词藻华丽的。孔子还有一个可敬之处,那就是他对外在表现的天生敌视,因为这种外在表现在朴质方面毫无惊人之处,倒是更着意于使人过分媚俗。 [177] 孔子相信,真正的君子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身体舒适和拥有财富。 [178] 孔子说:“如果财富是我所寻求的正当对象,我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得到它,哪怕是不得不去做个挥鞭的车夫。但是,如果它不是合适的目标,我将遵从我爱好的东西。” [179]
从孔子的所有这些言行当中,我们能够很轻易地得出结论说,孔子是个禁欲主义者,但是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180] 因为真正的禁欲主义者通常把享乐本身看作是罪恶的,并且可能甚至认为痛苦即是善。但在孔子那里却没有这些。实际上,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儒学从未反对过中庸适度的身体享乐,而孔子本人也并非不同意娱乐,除非它与德行和真诚不相一致,甚至相反。孔子称赞将学习作为一种乐趣,并把音乐看作是纯粹的娱乐之源,这是很独特的看法。 [181] 孔子对管弦乐有浓厚的兴趣,并且自己能够弹奏一种古琴(瑟),他还参加非正式的合唱。 [182]
在古代中国的主要哲学流派中,儒学的高明之处在于发现了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生理学事实:愉悦不只是一种生活追求,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他的每一家哲学(具有不同表现方式的某种程度的极权主义倾向)都对娱乐本身,至少是对普通人的享乐大皱其眉。墨子和他的学派大声反对生活中的各种修饰和不能直接产生经济价值的各种行为。 [183] 道家著作《老子》也同样谴责生活修饰,希望人们做到“无欲”。 [184] 羽翼丰满的极权主义者——法家人物坚信人们只是国家的器官或工具,所以,人们不应该拥有个人的思想和情感。一位法家人物甚至坚持认为,应该把人民的日常生活弄得了无趣味,致使他们欢迎战争,在战争中解除无聊。 [185]
然而,孔子却认为,如果一个政府不能使它的人民幸福,它就是不合格的。 [186] 孔子还特别嘱咐他的学生,在规划他们的日常生活时,要包括休息和娱乐。 [187] 编成于汉代的《礼记》讲了一个故事。虽然此书无疑是不足以完全凭信的,但这个故事却是对孔子有关态度的正确理解。故事说,弟子子贡在年末参加了一次农业祭祀,当他看到人民的狂欢作乐后,便抱怨说他们看上去太疯狂了。可是(据此故事说),孔子却告诉子路,应该理解他们只是在漫长的几个月的劳作之后作一些必要的休息和娱乐;要记住,即使是一张弓,也不能总让它紧绷着,而有必要让它松弛一下,以便恢复力量。 [188]
儒学之所以具有魅力,其隐密的真义之一,就是这种对于普通男女之感情和需要的同情。平衡是需要的,即一方面避免过度放纵的享乐,另一方面避免无意义的苦行,这是典型的孔子性格的体现。作为一位天才(他确实如此)和具有创造精神的伟大领袖人物,孔子确实是卓越地把持住了这种平衡。
孔子认为,在他那个时代,人类文明的命运如何,完全要依赖他自己的努力和成功。在情感层次上,他对于完成这一使命具有高度的自信。 [189] 孔子的保证是那样的真确,以至于即使是不公正的批评都不能烦忧他的这一追求,并能以微笑面对。 [190] 不过,孔子并未装作无所不知,他明白,在任何一位学者的词汇表中有几个字是基本的,即“我不知道”。 [191] 孔子通过提问题来寻得信息,而并不在乎这会使别人认为他无知。 [192] 如果学生的意见与他的观点相左,孔子不仅不会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冒犯,还会承认他们的不同意见是正确的。 [193]
虽然孔子确信自己肩负着巨大的使命,但他还是相当谦逊的。 [194] 尽管他不断强调人们真正关心的应该是实在的成就而不是荣誉,但他还是相当关注人们对他的看法,并有时还在他的一些亲近弟子面前抱怨说,没有人能够理解他。 [195]
促使孔子的情感倾向于他的同胞的东西,或者是促使他努力使别人认为渺小的而他却能显现出伟大的东西,既不是他对自己之重要性的信心,也不是他所缺乏的现实政治中的成功。孔子既和蔼可亲又善解人意。据记载,在招待一位眼睛失明的客人时,孔子细心地把这位客人介绍给在场的每个人,并向客人说明他可能感到好奇他看不着的所有东西。 [196] 孔子以足够的仁慈更关心人类的福祉而不是财富。“马厩着火后,夫子从宫中一返回就6问:‘伤着人没有?’他并没有问马的情况。” [197] 在田野里进行户外活动时,“夫子只是垂钓,不用流网拦捕;射箭时,不射杀正在孵化的鸟儿”。 [198]
孔子明确肯定了年轻人的远大前途,这使他赢得了各地青年的感激。孔子说:“一个年轻人应当受到绝对的尊敬。你怎么知道有那么一天他不会完全达到你现在的程度呢?一个到了四五十岁还无所作为、显现不出自己的人,是不值得尊敬的。” [199]
这种不同寻常之人可能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一个具有幽默感的狂热者(这差不多是个自相矛盾的评语)。就我们所知,孔子并不常讲笑话,但却一定经常眨眼睛,他所说的许多事情有一种不马上显露的幽默之处。当然,孔子的幽默有时也会让用心善良的解释者做出糟糕的评论,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断然认为,开玩笑有损于圣人的尊严。
孔子的一位同代人以极尽挖苦的口吻指出:“孔子的确伟大啊!他相当博学,然而他却没有在任何行当中使自己出名。”孔子闻听后,并没有指出以下事实为自己辩护:作为教师,他获得了不可忽视的荣誉。相反,孔子欣然接受了这个严肃的批评,并对弟子们说:“现在让我来看看,我将动手干些什么呢?去赶车呢,还是射箭呢?我看还是去赶车吧!” [200] 大多数注释者都非常不情愿看到孔子对这种荒唐批评所予以的冷嘲热讽式的回答。他们极其严肃地看待整个事件,并坚持认为孔子所作的是“对赞誉的谦逊回答”。 [201] 因此,这段话的头几个字,“孔子的确伟大(大哉孔子)”还被一些人用大字书写,挂在墙上,作为赞美圣人的箴铭。更有甚者,在《论语》的记载中,即使孔子特别指出他在开玩笑时,一些注释者仍然拒绝相信。 [202]
然而,孔子既不是圣人,也不是完人。如我们多数人所做的,他生活在那个社会中,就要依照那个社会的社交常规行事。为了应付某种特殊场合,孔子也得说一些缺乏实在内容的套话,但其目的不是欺骗而是尊敬听话者的颜面。有一次,一个人想见孔子,孔子却明确地予以拒绝。“孺悲想会见孔子,孔子拒绝了,理由是他病了。但是,当传话人出门时,孔子弹着琴瑟唱起了歌,以保证让来人听到。” [203] 这说明他不是不能见,而是不想见。
孔子的自制力是了不起的,但却不是超常的。虽然他认为情感应该有所节制,但他心爱弟子颜回的去世却使他悲痛难忍。其他弟子告诉他:“您过分悲痛了。”而孔子却回答说:“是真的吗?如果我不为这个人过分哀伤,那我为谁才能这样呢?” [204]
据记载,有一次,孔子对一个粗鲁无礼的熟人发了火,以至于到了“用手杖击打他的小腿”的地步。 [205] 孔子生活中的可叹行为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不能把这些内容从《论语》中除去。因为,正是这些内容才使得孔子成为人。
第六章 弟子们
如果我们要了解身为教师的孔子,就必须先得弄清楚孔子的学生是什么类型的人,因为他们与孔子朝夕相处,与孔子有过最多的直接交流。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些弟子的数目被严重夸大了,以至于达到了3000人之多。而《孟子》和一些别的著作认为他们共有70人,这可能是弟子数目的最上限。 [206] 即使是为了接近这一数目,几乎被提到的与孔子有关的每个人都被看作是弟子了。因此,《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竟把公伯寮也算作孔子弟子了,此人只在《论语》中被提到,说他是子路的政治对手。 [207]
不过,即使是《论语》提及的请教过孔子的人,也不好被认定为弟子。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书提到的大约22人是孔子弟子,但其中也只有一部分人达到了清晰可辨的程度。
当代中国学者钱穆指出,孔子弟子可以分成两部分,即孔子最后一次离开鲁国去周游列国之前进入孔门的早期弟子(“先进”弟子),和孔子最后归鲁后收授的后期弟子(“后进”弟子)。 [208] 可是,要想把这两个集群精确地划分开来并不容易。一些看上去属于后期的弟子,严格说来恰恰是在孔子出发周游之前进学的;而一些早期弟子,当孔子晚年时仍在门下。至于每位孔子弟子的确切年龄,我们几乎找不到非常可靠的材料,《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说的弟子年龄仅仅是一种观点,而崔述认为,这些年龄的精确性是值得怀疑的。 [209]
传统说法认为,子路很可能是最年长的弟子。有时,子路不像是以孔子学生的面目出现,而更像是孔子“最好的朋友和苛刻的批评者”。我们曾见过,孔子与南子的会见使子路大为震惊。还有两次,当孔子考虑参加据邑而反的叛乱者的行动时,子路表示坚决反对。子路严格要求自己,据说他“从未忽略过对别人的许诺”, [210] 而孟子则说:“当有人指出子路所犯的过失时,他大喜过望。” [211]
尽管具有这份直率和正直,子路还是弟子中最温情和仁慈的人物。或许有从军的经历,使子路养成了军人的性格。因为子路有治军的才能,孔子就举荐他做官,并且公开说:“像子路这样的人,从不会自然死亡。” [212] 许多弟子礼数周到,具备了学者的翩翩风度,而子路则因为性格刚直、情绪急躁,使得自己根本达不到这样的高度。这种状况使子路产生了一种浮躁的情绪,那就是拔高他的禀赋,以至于自夸他明知自己拥有的那些品质。因此,当有一次孔子称赞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的才能时,子路大声说道:“好吧,如果您要率领一支大军,您想和谁在一起呢?”孔子答道:“我不要这种人跟我在一起,他们(如《诗》所说)‘赤手空拳斗老虎,不乘舟船过大河’。我想要的那种人是,他们谨慎地迫近困难,并制订周密的计划以取得成功。” [213] 可怜的子路总是因鲁莽而受责。有时,孔子明确地给他布下陷阱,而他总要踏进去。一天,孔子说:“如果我的学说再没有进展,我将坐着筏子漂流到海外去。子路,我相信你会与我同行的。”子路对此信以为真,表现得非常高兴,这使得孔子不得不冷峻地加了一句:“子路比我更喜好勇力,但却不会去运用判断力。” [214]
子路的言行不可避免地为自己招来了大量的批评。实际上,尽管他具有坦率的长处,但却远远达不到孔子所要求弟子的理想行为。不过,孔子也颇为小心,尽量弱化对子路的批评,以免伤害太深。 [215] 虽然(或者可能是由于)他们的脾性极其不同,但在孔子与子路之间却有着坚强的联系。孔子在不断尽力抑制子路的过度热情的同时,也完全欣赏他这位高大强健的信徒的靠得住的品质。像颜回一样,子路分担了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所遭受的磨难。而真正的问题是,孔子是更喜欢颜回(他经常受表扬)呢,还是子路(他几乎总是受批评)呢?正如孔子所设问的:“爱,不是总能导致对于所爱对象的严格要求吗?” [216]
孔子和子路回到鲁国之后,西元前481年,有一个事件暴露出子路和冉求的鲜明不同。鲁国的邻国小邾国有一位官员(他控制着一座城邑)来投奔鲁国,提出的附带条件是他把这座城邑献给鲁国,以换取鲁国保证他的安全。这种事情在当时是相当常见的。这样的协议通常是用盟誓约定来加强的。但不同寻常的是,这位官员不要求与鲁国政府的盟誓约定,而是仅仅要求与子路订立一个君子协定。无论子路是否再次从政,此时子路肯定是在鲁国,但子路认为这种要求是对他的侮辱,就拒绝会见小邾国的那个人。于是,季康子就派冉求去说服子路。冉求请求道:“此事怎么能是对你的羞辱呢?他是因为不相信大国的誓约,而只相信你的一句话呀!”子路回答说:“如果鲁国与小邾国开战,我将不问敌对行动的原因,而情愿拼死在对方城下。但这个人是他的君主的叛臣,而你们却答应他的要求,把他当成正人君子来看待,这是我做不到的。” [217]
此后不久,子路带着他的被保护人子羔(高柴)去了卫国,一起供职于孔氏(悝)。孔子在卫国时,与孔悝和他的父亲孔(圉)文子有过交往。当叛乱给孔悝带来严重危险时,子羔逃跑了,并力劝子路一同逃走。子路却回答说:“我吃人家的俸禄,不能在人家遭遇不幸时逃走。”子路力图去救援其主人,却被敌人用戈击杀了。 [218]
冉求也是早期弟子中的佼佼者,但他的性格几乎与子路正好相反。冉求没有过度热情的毛病。相反,孔子有一次评论冉求说,有必要督促他向前,因为他遇事总是往后退缩。 [219] 在某一场合,冉求告诉夫子:“不是我不喜欢您的大道,而是我的力量不够了。”孔子答道:“那些力量不够的人,是一直走到走不动时才停止,但你却根本就没有启步。” [220]
冉求总是在动手之前就要冷静地掂量每次行动可能产生的利益。他是有才能的人,正如孔子某种程度上勉强承认的那样。 [221] 冉求也是个温和的谈说者,是一位老练的行政官员,甚至是一位称职的将帅。他的精明表现在,他挑选了有助于他的政治事业取得成功的路线。由于孔子的举荐,冉求得到了季氏的任用,获得了一个职位。但他很快就发现,正是季氏,而不是孔子,能有助于他在政坛上的步步高升。因此,冉求竭力推行季氏的政策而不是孔子的学说。自然而然,在季氏面前,冉求日渐受宠,而没有指望的子路则受到冷落。为此,孔子变得对冉求越来越不满。所以,当冉求帮助季氏增加会使人民负担更加沉重的新税赋时,孔子就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弟子了。可是,并未看出他事实上被(至少是很长时间地)逐出孔门。
子路之丧生是因为他拒绝擅离职守,尽管当时的力量对比对他是无望的。可是,数年之后,当我们再次看到冉求时,他却依然飞黄腾达。 [222] 对于这其中的道德寓意,我们必须留给伦理学家去分析和评判。
乐居性情之中游的是弟子子贡。他具有一种幸运的才能,使他能够取悦于他为之工作的那些人。他为他们工作,但却不必奉承他们;他也获得了成功,但不必抛弃他的原则。可以说,子贡是那种具有良好适应性的人,能够把内在和外在的东西结合起来。一定程度上讲,子贡是有主见的哲学家,然而,他那开朗的性格又使他左右逢源,让每个人都喜欢他。在日常讲话中,子贡能充分表现他的口才;作为外交家,他又是那样地善于应对,以至于季孙曾后悔没有带着子贡就冒失地参加了一次外交盟会。面对棘手的政治事务,人们渴望得到子贡的判断。甚至在经商方面,他也获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 [223]
《论语》清楚地显示了子贡与孔子之间极其亲密的关系。可能是因为这个事实,以及他的资历和才能,在孔子死后,子贡被看作是为孔子守丧期间的孔门主持人。 [224] 子贡对孔子的忠诚是坚定不移的。在两个场合,有些人(一次是弟子子禽)认为子贡与孔子可以平起平坐。但这两次子贡都十分肯定地解释说,这种断言只能说明讲话的人缺乏理解力。他警告子禽,最好是小心说话,以免让自己担上蠢人的名声。 [225] 子贡宣称,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什么人能与孔子相提并论。 [226]
孔子称赞子贡的才智,并把他作为有政治洞察力的人推荐给季氏。 [227] 但是,孔子也被子贡气得够呛。孔子总是怀疑辩才,而这正是子贡所擅长的。利用他随和的性格,子贡一定会成为一个不怎么使人感到厌烦的人,再加上他丰富的天赋魔力,成功就属于这位文雅的弟子了。毫不奇怪,孔子对他没有办法,只好在忍不住一时冲动的时候,用暗中讽刺的方法揭穿子贡的自恃。 [228] 看着子贡,孔子特别为颜回感到苦恼。颜回被认为是所有弟子中绝对最有才能的一位,但却既无名声,又无家财,而子贡和其他人却轻易赢得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成功。 [229] 孔子有一次问子贡:“你认为你和颜回谁更强一些呢?”子贡回答说他不敢与颜回相比较。 [230]
颜回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但在其他人眼里,确实是不知怎么称赞他才好。对于颜回的称赞,《论语》中有很多说法,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加在一起时,得到的仅仅是个德行操守条目。孔子自己承认说:“直到我们了解了一个人的过错,才能断定他是有德行的。” [231]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这句话,就会很容易怀疑到颜回,证明他是具有严重缺点的,因为他几乎不犯什么过错。同时,与某些弟子不同,我们几乎从未看到颜回说些什么,通常他刚好与孔子保持一致,或者不加评论地接受了孔子的决定和意见。人们不禁要怀疑,颜回是否只是个根本没有主见的蠢材。
颜回几乎从未表现出过温情,也没有通乎人情的态度。有一次,颜回和子路与孔子在一起,孔子说:“为什么不向我讲讲你们两人都想做些什么呢?”子路马上回答:“我想拥有车、马和裘皮衣服,并与我的朋友分享,而不在乎朋友们把它们弄坏。”颜回则说:“我的愿望是,不自夸我的长处,也不过分强调我为别人做过的事情。” [232] 这让子路颇感难为情,就很快请老师也说说有什么愿望。不过,如果有人认为颜回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完全没有同情心的人的话,那也是错误的。子路是个可爱的人物,但他永驻的孩子般的自夸和对于受表扬的渴望,在那时一定很难与人相处。
孔子本人也曾惊诧,是什么东西使得颜回如此不同寻常地温顺。孔子说:“我整天跟他谈话,而他从未有过与我不一致的地方,这样看上去他好像是个愚人。但是,当我探查我不在场时他的作为时,我发现他的行为完全证明了我教给他的东西。不,(颜)回不是愚人。” [233] 不仅是孔子,其他弟子也称赞颜回,称赞他杰出的才智和德行。 [234] 孔子对颜回的称赞完全超过了其他所有人,称赞他既是勤奋的学生,又是不屈不挠地坚持道德行为准则的人。 [235]
不过,颜回显然不曾得到过行政职位。 [236] 他的去世确实相对早一些,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当时没有一个在位者对颜回感兴趣,因为适合他们兴趣的是其他弟子。 [237] 孔子则说,颜回和他一样没有被任用。 [238]
如果颜回未能从政的原因是由于某种缺陷,那么这种缺陷不是才智上的,而是个性上的。颜回终其一生都很贫穷,这一事实作为一种天然的限制,会使他变得很拘谨。孔子宣称,在直面其他人不能忍受的贫困时,颜回“坚持一种不变的快乐”。 [239] 但在经过了一定的时间之后,这种快乐就变得有点机械了。如果我们一定要确保对人类精神的至高无上的考验的话,上述变化便是特别真实的。这种考验就是,眼看着那些在才智和才能方面远比不上我们的人,再三再四地优先于我们被任用。这就是颜回的命运,也正是孔子的命运。但孔子能够升高到完全超乎其上,这就是为什么他是所有时代的伟人之一的部分原因。要是颜回(更像我们其余的人)因此而有点性格乖僻的话,我们也是很难责怪他的。
孔子把颜回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 [240] 当他去世时,孔子呼喊道:“上天在毁掉我(天丧予)!”并以在其他场合不会有的举动来哀悼颜回。 [241] 颜回家境贫寒,家中无力给他以厚葬。其他弟子们便合力以时尚的标准厚葬了他。孔子反对这种厚葬,因为这与贫穷之家不相称。弟子们怀着深深的敬意以及(也可能是)慰藉之情埋葬了颜回。教师得意门生的位置是最难待的。
其实,并不是所有弟子都能成为我们所讨论的那些少有的杰出弟子。宰予便以其绝对的难以驾驭而把自己从这样的弟子中区分出来。宰予不仅与其他人不同,甚至还微微刺破了蒙在孔子箴言上的有趣的薄纱。 [242] 要是他有突出才能的话,这种做法可能还会得到完全的肯定,但他并没有像样的才能。 [243] 宰予是能言善辩者,这似乎是他唯一的长处。孔子说:“从前,我只要听到人们说的话,就肯定了他们会付诸行动。但是现在,我听了他们的话之后,还要审视他们的行为。我从宰予那里得到的经验导致了这个变化。”宰予也很懒惰,多次使孔子难以忍受到了顶点。 [244] 不过,我们发现了宰予与鲁(哀)公的会谈, [245] 而这份殊荣从未落到过颜回的头上。
后期弟子极其重要,因为正是通过他们,孔子的学说才传至后世。这些后期弟子没有一个人像子路、冉求和子贡那样达至政治高位。但是,孔子并没有用他或他的弟子们的政治活动去深刻地影响世界。确切来讲,孔子用来影响世界的是他的思想学说。孔子的学说之所以能够生效,正是由于弟子们宣传了它,并且大抵是后期弟子担当了这方面最重要的角色。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他们后来所教授的与他们先前从孔子那里所学的并不完全一致。这些人塑造并给定了儒学原理和儒家传统的首次取向。因此,我们必须探究他们是何种类型的人。
无论依据什么样的重要标准,都不容易确定究竟是哪位弟子做了教师。与此相关的种种传统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 [246] 崔述(可能他掌握的证据与别人一样多)认为主要的宣传家(传播者)是子游、子夏、子张和曾子。 [247]
如果只是根据孟子所述的令人好奇的故事,我们必须要提及另一位后期弟子。孟子说,孔子死后,子夏、子张和子游“认为有若好似圣人”,并希望能像侍奉孔子一样地师事于有若。他们力劝曾子参加,但被拒绝,因为曾子宣称,没有人堪与夫子相提并论。显然,这个计划最终破产了。 [248] 有若可能有自己的学生,因为《论语》中有三次提到他时均称呼他为夫子(有子),但我们对他知之甚少。
有关子游的材料,我们只有不多的一点。他被称赞为在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成就。 [249] 像其他后期弟子一样,子游对礼乐特别感兴趣。《论语》记载,当孔子走近子游担任邑宰的城邑(武城)时,听到了弦乐和歌唱声。寻声而去,孔子发现,原来是子游正在教授当地人音乐和礼仪,而这些通常是朝廷中的君子专用的。子游解释道,他这样做是把孔子之道教授给人们。这使子游成为平民教育的最早实践者。 [250]
子张是后期弟子中最为精神饱满、冲劲十足的。事实上,孔子有一次说他是失之于“走得太远”。 [251] 子张坦诚地钻研赢得官职和俸禄的方法,并希望自己能够成名。 [252] 他没有那些热心于追求大道的人们的耐性。子张宣称,如果有必要的话,人们应该时刻准备着为他们的原则而献身。 [253] 这个精神饱满、一往无前的弟子并未受到同门的完全欢迎。曾子认为他是自我看重,而子游则说:“我的朋友(子)张能做困难之事,但他不是完全的讲求德行之人。” [254] 《论语》并未直言子张有自己的学生,但《韩非子·显学》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都把子张列在了孔子死后从事教学的弟子之中,前者还认为他是儒家内部一个学派的创建者。
《论语》特别指出子夏有弟子,并讲述了与他的教学活动有关的事情。《墨子·非儒篇》中有墨子与子夏弟子的一场谈话。《史记·儒林列传》则告诉我们有四个人跟随子夏学习,并在后来“成为王侯之师”。子夏自己到晚年也是魏文侯的私人教师。 [255] 毫无疑问,在传递和建立儒家学说的人们之中,子夏是非常重要的一位。
子夏有一些学究气。 [256] 在《论语》中,他被称赞为文学之士。孔子认为他的脾性与子张相反,说子张走得太远,而子夏走得还不够。此二人的不同达到了言语冲突的地步。有一次,子夏的一位弟子向子张请教与人交往的原则。子张问道:“子夏告诉你们些什么?”这位弟子回答:“子夏说:‘与那些行为得当者交往,与行为不当者保持距离。’”子张说:“这与我所讲的不同。君子褒扬有德有才之人,但却宽容所有的人。” [257]
这种争论大量涌现在孔子死后。正如《韩非子》所言,从事教学的每位弟子都自称拥有“真正的孔子学说”,而既然孔子“不能死而复生,谁将作孰是孰非的裁定呢”? [258]
子游说:“子夏的弟子在以下方面做得足够好:洒扫地面、应接传唤、回答提问以及举止进退。但这些事情是特殊的和偏专的,而与基本要求相关的东西却相当缺乏。”子夏为自己作了辩护,宣称不能一下子教授给学生全部真理,而应该是循序渐进地加以传授。 [259]
可是,如果说子夏只是个学究,在其他方面一无所能,那将是错误的。子夏曾做过一个城邑(莒父)的邑宰。 [260] 他兴趣广泛,有一些见解还使孔子受到启发。不过,子夏确有某种学究气质。比如,他认为:“只要一个人不越过大的道德问题的界限,就可以在小的道德问题上有所出入。” [261] 这显然证明了,他以命令式的言辞把道德准则认作是某种僵硬而固定的规则,而不是像孔子那样,把道德准则看成是达到某种目标的实际进程。可能正是这些倾向,促使孔子提醒子夏一定要以“君子的而不是小人的方式” [262] 行事。
如同其他弟子的情形一样,在种种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子夏的轶事,这些书籍的年代晚于我们现在使用的主要材料。例如法家著作《韩非子》,其中引用的子夏言语完全是法家式的,以至于让人马上就会怀疑子夏不是个忠实的儒者。 [263] 这种让人在身后改变信仰的做法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常见标识。后来的儒家书也包含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孔子弟子的故事,其中有一些可能是真的,而另外一些确实是虚构的。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几乎不可能从所有后世著作的伪造资料中区分出真实的东西。为此,我们只能在较少的著作中寻找实情,因为这些著作是早期的记载,更为可靠一些。
另一位具有巨大影响的弟子是曾参。 [264] 《论语》通常称他作曾子(曾夫子),因为这种称呼是他的弟子对他而言的,所以,至少在表面上看去也可以说曾子一派主要掌握了编纂《论语》的工作。孟子把曾子称作老师(先生),并说有一阵子曾子有多达70多位学生。 [265]
孟子也认为曾子是无畏的,但在一则故事中,孟子所讲述的曾子的行为可并没有表现出这一点。孟子说,曾子居住的城邑遭到邻国军队的袭击,而曾子则是第一个跑掉的,为此,他显然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孟子为曾子受到行为怯懦的指责作辩解,说既然他不是士兵,也许这算不了什么。然而,更重要的是,曾子在袭击到来之前离开城邑时还告诉看房人,“不要让人住我的房子,他们可能会毁坏草木”,这种话完全缺乏仁爱之心。 [266] 无法想象曾子会说出这样的话。
可是,如果说曾子不重视道德之行,那将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除此之外,他根本就别无他顾。我们发现,在《论语》所记载的曾子的许多观点中,与世俗的国家或政府的行为相关的内容实在是很少,而是绝大部分专注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当曾子病重时,孟孙来看望他。曾子说:“一个人临终之时,他的言语是善良的。一位君子,遵从着大道,把三样东西看得高于一切:他的每个态度和每个姿势都远离暴力和傲慢的迹象;他的每个面部表情一定预示着善良的信仰;他说出的每个字一定要去除粗野和不得体的痕迹。” [267] 令曾子感到宽慰的是,面对死亡,他马上就要超越那种只有在活着的时候才可能做出的不得体举止的危险了。 [268]
曾子因为对孝的博学深思而在儒家之中受到欢迎。 [269] 在《论语》的好几章中都有曾子对孝道的阐述,而孟子则以带有某种程度的传奇色彩的方式描述了曾子的不同寻常的孝行。 [270]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正是后期的而非前期的弟子对孝给予了特别的注意。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出乎人们的预料。
被看作是两个集群的早期和后期弟子在个人兴趣和实际行动方面有着显著的不同,而孔子的个人经历的确是导致这种不同的部分原因。我们看到,直到他周游列国的最后幻灭到来之前,孔子还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一个官职,并以此实践他所宣讲的政治和道德思想。在他晚年回到鲁国之前,孔子只是偶尔搞搞教学,而真心等待的却是再造世界的伟大机遇。在这种等待的间歇之中,孔子也乐于告诉那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如何去做那些他自己正在筹划着的事情。孔子教授的这些弟子是热情澎湃的。但是,当他不得不面对政治机遇不再到来的事实之后,晚年的孔子便自然而然地把主要精力转向了书本和教学。如果他自己不能救助灾难深重的世界,就得教给别人今后如何去做。早期弟子竭力效仿早年的孔子。他们期望有效地参与实际政治的运作,而其中一些人也确实能够做得到。然而,大部分后期弟子则努力效仿晚年孔子的作为,但这并不是孔子希望弟子们全力去做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后期弟子的主要兴趣在于教学、礼乐,在于给个人而不是给全社会灌输道德。所以,与孔子(Confucius)本人的思想相比较,孔子主义(Confucianism,儒学)具有更少的实际政治改革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之热情的痕迹,但却被打上了更深的学究式的拘泥于礼仪的烙印。这是为什么呢?以上所述前、后期弟子的不同追求应当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第七章 教师
自古以来,教师的数目可谓不可胜数,但是像孔子那样以个人的身份并完全依靠对年轻人的教导而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教师却是屈指可数的。孔子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依靠的是他特殊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
在孔子时代之前,中国就产生了兴办教育的活动,但我们对其具体内容却知之甚少。确实有一些典籍认为,在孔子时代的几千年前就有了真正的学校在运作,但大部分这种书籍都完成于孔子时代的几个世纪之后,所以它们之中有关学校教育之记载的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 [271] 生活在孔子去世一个世纪之后的孟子认为,在周朝的上两个朝代——夏朝和商朝,都建立过正规的学校。 [272] 但孟子并不能被免除以下的怀疑:他想把在未来要完成的东西归之于过去。当我们转向实际上出自前儒家时代的文献时,就会发现,除了那些用来教授射箭的地方外,没有证据证明有过任何正规的学校。这种教习射箭的地方是青铜器铭文提到的。 [273]
可是,根据可靠的记载,有大量的人跟随私人教师学习。很可能是,所有具有世袭特权的将来的统治者,以及也许是所有高层贵族的子弟,都有私人教师。官阶低的年轻人要接受比他们地位高的官员的训练,但是,这些教育渠道与孔子的教育举措不是一回事。负责这种培训的教师事实上是政府官员,接受教育的人是那些已经在政府任职或者注定要继承政治地位的人,而对这类人的培养目的也是贯彻与现存政治模式相一致的政府(官方)行为。
孔子所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作为平民的个人行为,孔子把各种条件的人都当作他的学生,只要他们是块好料。孔子教育他们的意图是:造就一个不同的,并且是他所深信不疑的、非常良好的那种政府。
所以,孔子的教育目标是实用性质的,但是这种实用性并不是狭隘的实用主义。尽管教育的目的是造就良好的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的最终结果仅只是培养一个称职的官吏。事实远非如此。孔子所要培养的官吏在各方面都应该尽善尽美,近乎理想之人。他们绝对不仅仅是具有某种特殊技能的专门人才。 [274] 孔子有一次把完人定义为这样一种人:拥有智慧,脱离贪欲,勇敢无畏,多才多艺,以及彬彬有礼,精通礼仪和音乐。 [275] 这无疑是他摆在学生面前的做人的典范。
孔子希望他的学生所具有的某些品质,例如勇敢和诚实,并不是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但是,孔子的目标不是个人成功的事业,而是良好的政府。他相信,只要政府由某种人进行管理,这个目标就能够实现。这种管理政府的人一定要接受通常所必需的教育,还需要具有刚正不阿的品质,以及达到自我约束的修养。孔子问道:“一个不能自我克制的人怎么能够管理他人呢?” [276] 事实上,孔子认为,国家首脑和所有政府官员在道德上都应该成为最高行为方式的典范。他进而强调,如果国家的管理者想取得实实在在的政治成就,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模范作用,而不是花样繁多的说教或惩罚。
在这方面,孔子常常被误解。不可忽视的是,后来(我们以汉代为一个特别分界)开始流行一种形而上学的,或者也许应该称作伪科学的理论,认为宇宙的各个部分之间都以亲密的和显著的方式相互联系。在这种形而上学理论看来,皇帝的最微不足道的行为也会影响宇宙的运作机制。因此,成书于汉代的《礼记》说,如果皇帝在夏季最后一个月穿白衣而不穿红衣的话,“大地将一片汪洋,庄稼不会成熟,还会有许多妇人流产”。 [277] 许多学者以这种形而上学理论解释孔子的思想,认为他所讲的对统治者德行的本质性的影响就是指的这种几近魔法的强制力量。 [278] 本书作者从前就持这种观点。 [279] 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真正的早期文献,就会发现这种思想与前儒家思想并不相干,也没有出现在哪怕是稍晚于孔子的著作中。这并不是说在早期著作中就没有迷信或异教。在许多早期著作中有大量的(但却是不相同类型的)神灵和精怪,它们是那样的实在,以至于有时会产下婴孩,但却并不带有神秘的和复杂的“感应”作用。总的来说,在早期文献中,孔子认为,统治者要想引导人民趋向于善,就不能依靠魔法般的强制力量,而是一定要依靠道德典范的力量。 [280]
孔子尽力使他的学生(有一些来自社会下层)成为适合于担当(严肃意义上的)政治职位的人。也许正是为此原因,孔子号召他们修养理想的人格,要求他们努力成为“君子”。“君子”这个词的字面意义是“国君之子”,也就是国君的亲属,因而也是贵族的一员。与之意义相反的是“小人”,意指平民百姓。 [281] 在早期文献中,讲到有继承权的贵族时,一般都是使用“君子”这个词。在早于孔子的文献中,“君子”也很少有其他意思。 [282] 孔子有时也使用这个词的旧有意思,但是,对他来讲,这是例外的用法。 [283] 在通常情况下,孔子所说的“君子”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们具备了一个理想的贵族应该拥有的那些品质,也就是说,孔子的君子,是一个真正的(而不仅仅是世袭的)高贵之人,高尚之人。这个词的词义变化类似于英文的gentleman一词。这个词原指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人,但现在一般是指举止得体和有修养的人,与人的出身并没有关系。为此,我们就遵循常规,把中文的“君子”译作gentleman。
因为“君子”的新意义而不是旧意义逐渐流行起来,所以,那些不符合儒家行为标准的在位者便自动将自己划入了“非君子”的行列。这样一来,儒者便指出,正是君子,而不是世袭的在位者,才是真正的高贵之人,并且因此而理应成为政府的管理者。
孔子的目标是把他的学生培养成君子。孔子是用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实现这一目标的呢?他自称从未拒绝过教授任何人。尽管他很穷,孔子也只要求他们带一束干肉作为投师的礼物就可以了。 [284] 这不仅仅是自恃,还有儒学所坚持的对卑贱之士的善待,而这种亲切的接待表现在《孟子》里的一个有趣的故事中。在他的时代,孟子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周游列国。有一次,孟子访问一个国家时,居住在该国的一处宫殿里,可是这个宫殿的管理人却怪罪孟子的弟子偷窃了他的一只尚未编好的鞋子,孟子因此而被深深地激怒了。可是,这位管理人为自己的猜疑作辩护说,众所周知,孟子不加调查地接收任何想跟他学习的人。 [285]
无论是贫穷还是卑贱的出身,都不会成为跟随孔子学习的障碍,但这并不是说孔子就没有其他条件了。孔子声言拒绝教授蠢材,并宣称他要教诲的是“那些满怀渴望”想受到启迪的人。 [286] 孔子提出这些条件的意图,可能是想避免在这样的学生身上浪费时间,他们跟随孔子学习的目标仅仅是获得财富和地位。这些人借口关切较高层次的事物,实际上却为破衣烂衫和粗茶淡饭感到羞辱,就这样,孔子因为他们“不值得交谈”而打发走了他们。 [287] 可是,孔子也悲叹“很难找到情愿学习三年而不想获得任何物质报酬的人”。 [288]
那些在附近没有家的学生可能就住在孔子的住所里。 [289] 孔子的教育方法完全是不拘形式的,所有的记载中都没有提到分班或进行考试。相反,孔子同时与一位或几位学生在一起交谈,有时自己讲,有时提问。对于书本,孔子要求学生们自己去读,但也建议他们应该在一起学习和讨论那些特别的章节。尽管这种个别教学法现在不被广泛使用(因为它费用太高),但却酷似于在一些学院和大学里采用的导师制。
这是孔子成功使用的一种独一无二的教学方法。因为孔子不仅仅是一位从事教育的学者,而且还造就了有能力在世俗政治事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君子。孔子不教授固定的课程,但却有确定的学生。所以,孔子的方法是强调因材施教。既然每个学生提出了不同的难题,那么,对每个学生就应该有不同的对待。 [290]
因此,在这样的教学活动中,第一项任务就是把握每个学生的理解力和所达到的程度。正如每个好教师一定会做的那样,孔子十分留意学生的性格。 [291] 他的手法之一,使人想起现代精神病疗法,那就是:让他的学生们心情舒畅,然后再要求他们自然地和没有保留地讲出各自的志向。在这种场合,孔子是个良好的倾听者,当弟子们发言时,他不打断也不加评论地聆听。这样做的时候,他只是独自微笑。但是,在他们讲话的同时,孔子已经把整个印象贮存起来,琢磨着如何提高他们的长处,克服他们的缺点。 [292]
一旦做出了对某个人的分析,孔子就依之确定他的教育方法。有时,同样的问题,对不同的学生却有着不同的答复。有一次,子路问孔子,当他学会什么时,是否应该马上付诸实施。孔子告诉他不可以,应该先去跟他的父亲和兄长商议一下。随后,冉求也来问同样的问题,孔子告诉他可以,应该马上去实践他刚学会的。弟子公西华得知了这两种不同的答复后感到很困惑,就请教这种不同的原因。孔子告诉他:“冉求缺乏激情,所以我鼓励他;子路急于显示自己的力量,我就劝阻他。” [293] 事实上,这种教育方法与两位弟子的性格表现是一致的。
孔子教学方法的不拘陈式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不久之后中国的教师们却竭力拘泥于他们自身的威严,并且要求他们的学生不加怀疑地接受他们所说的一切。可是,孔子以平易近人的态度对待学生,也并没有后代教师们的令人震惊的清规戒律。这种区别不是偶然的。孔子的态度和教育方针与他的政治哲学和知识论是一致的。孔子强调的不是对错误做法的惩罚,而是对正确做法的鼓励,不是强制而是说服。对待任何人和事,孔子都是坚持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态度。 [294]
孔子的做法与后来墨子的做法是不同的。墨子的一位弟子抱怨老师强迫像他这样的新手节衣缩食(穿短衫、吃粗劣的菜汤)。 [295] 相反,孔子所看重的是获得学生的完全信赖。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孔子真的喜欢并尊重年轻人。 [296] 他对自己年轻时的困顿生活记忆犹新,他的态度就像是一位父亲、一位兄长或一位老朋友,他不想给他的弟子以神秘莫测的印象,而是宣称他对弟子们没有隐秘可言。 [297] 孔子不是不断地要求弟子们忠诚于他本人,而是给予他们更多的有关忠诚于自我的教导,他很少凭借对他们的出格行为的批评而“抛弃他们”。 [298]
无论如何,以师道尊严为基础的教师的权威在中国和儒学之中很快就变得闻名遐迩了。出生于孔子刚去世之时的墨子(他的哲学乃是源于儒学的一个分支)宣称:“我的话是适宜的指导。抛开我的话而自己去思考,就好像扔掉整个收成而去捡几颗谷粒。想用自己的话去否定我的话,就好像以卵击石,即使用尽所有的鸡蛋都不会损坏石头。” [299] 活跃在西元前300年左右的荀子是一位颇受欢迎的和有影响的儒者,他也曾经说过:“不尊重教师的正确方法而倾心于自己的方法,这好比是让盲人辨别色彩,或者让聋子区别声音一样,这是无法摆脱混乱和谬误的。” [300]
孔子不要求这样盲目信奉。实际上,因为他没有那些傲慢的确定性,所以,他不会错误地自认为拥有了绝对真理。孔子十分明智地知道,如果学生们不想做留声机,那就得学会自己思考。他们不能在自己思考的同时,又认为教师的每个字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学生与他不一致,孔子并不生气,有时他会坦率承认他们是对的而他自己是错的。 [301] 即使他确信他们是错误的,孔子也不想用书本的、古人的或自己作为教师的权威去强迫他们。孔子尽力用理性使他们信服,如果他不能让他们马上信服,就把事情先搁置一下,留待以后再讨论。 [302]
不过,所有这些并非意味着孔子是个随随便便的、不讲原则的教师,更不能说孔子对他的学生没有什么期望。相反,他对他们显然寄予了厚望。 [303] 孔子毫不松懈地对弟子们不断提出要求,以便使他们弄明白,他们必须亲自去完成的终极责任本来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304] 如果说孔子从未训斥过弟子,那是不正确的。我们已经见过,孔子甚至走到了不承认冉求的地步,这是因为冉求帮助富有的和有权势的季氏增加人民的税赋负担。可是,在通常情况下,孔子的责备是温和的,并且小心翼翼地不去伤害他所责备的学生的自尊。 [305] 孔子经常使用冷淡而缓和的幽默达到他的目的,比如说:“子贡经常批评别人。夫子说:‘显然子贡自认为已经相当完美了,以至于有时间花在这上头;我可没有那么多的这种闲暇。’” [306]
这种自由宽松的训导的结果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会让弟子们不守规矩和不受约束。当然,他们并不总是每时每刻都听从夫子,特别是在他们从政之后。但是,他们对孔子的忠诚和爱戴是始终不渝的,并且肯定是人类历史上不会经常出现的。孟子告诉我们说,即使是孔子经常斥责的弟子宰予(并且曾被认为责骂对他是不起作用的),也宣称孔子是曾经生活在世上的最伟大的人物。 [307]
孔子是用什么样的必修课程把所有的求学者(只要他们是有才智的和勤奋的)转变成“君子”的呢?从有关记载来看,尽管这样的课程不同于任何的现代教学课程,但也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对年轻贵族进行培训的学习内容。这两者的主要不同是,孔子的教学内容中去除了射箭和驾车。这两项技能原本是用于战争的训练,但在通常的贵族教育中是作为礼仪艺术来学习的。正如击剑一样,时至今日,还是欧洲贵族通常学习的技能。孔子自己受过射箭的训练,至少某些弟子也擅长射箭和驾车。孔子并不十分反对获得这些技能,但他并不教授弟子们,因为对于孔子意义上的“君子”来讲,这些技能不是必不可少的。 [308] 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一种征兆,那就是:孔子有意识地要把世袭的并且基本上是军事性的贵族政治,改变为具有良好品质和德行并且首要的是具有政府管理作用的贵族政治。
不过,中国贵族的另一门传统艺术却正好适合于孔子之教的目的。孔子把它拿过来,给予特殊关注,并使它发展成为几乎是儒家的标志。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礼”。“礼”有种种的英语译法,比如ceremonial、ritual和the rule of properiety。但是,在阅读和理解中国古代典籍的某些有关篇章时,这样的翻译不仅未能揭示出中文的本有含义,甚至还把它的真义弄得晦涩难解了。
汉字“礼”是个象形文字,表示的是一种祭器。它是个精致而贵重的器物,用来放置献给神灵的牺牲。我们不能怀疑这个汉字的最早的意义是“祭品”。事实上,在后来它也仍然保持着这个意思。这个意思的简单引申就逐渐地指祭祀时使用的礼仪了。
“礼”的进一步的发展模式就更复杂了。要理解它,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我们所谓的“宗教”和“世俗”在古代中国并不是完全分离的,事实上,它们几乎是纠缠不清地混合在一起的。同样,生与死也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青铜礼器通常是供奉祖先的,但某些器物上的铭文却告诉我们,它们既用于祭祀神灵,亦用于“宴请我的朋友”。 [309] 这使人想起,神的荣耀付与了罗马皇帝们,尽管他们还活着。 [310] 同样地,在早期中国文献的记载中,几乎用同样的词句祭祀死去的君主和礼赞活着的君主。 [311] 如果某个国君派出的外交使团尚在国外时国君本人就死去了,那么,当这个使团的主要负责人回来之后,要赶到陈放国君尸体的太庙里“向尸体汇报”。 [312]
在那个时代,宗教习俗关涉到生活的每个方面。在家族之中,祭礼并不是由专职祭司而是由家族首领主持的。如果是国祭,则由国君主持。军事征伐要在祖庙(显然,武器有时也贮存在那里)和“社稷”(土地神和谷神的祭坛)举行典礼;征伐结束时,要在祖庙向列祖列宗汇报他们的胜利,奖赏获胜的将军。 [313] 外交谈判会在祖庙里举行,因为人们相信,祖宗们都要真的到场。外交宴会也在这里举办。 [314] 甚至是求婚者也要被未来的新娘的父亲在祖庙、在神灵面前予以接待。 [315]
因为宗教典礼的范围是那样宽泛,所以,原本用来指明参加祭礼者的适宜的行动规则和方式的“礼”字有时被更广泛地用来指示一般性的适宜行为。这是个渐变的过程,并不会使人感到十分惊讶。在那些被认为早于孔子时代的文献中,汉字“礼”的使用并不十分普遍,然而在距孔子时代不太远的著作中,它却不仅有“祭礼”之义,而且在其中的三个例子里还有那种较广泛的意义。 [316] 这就是说,作为行为名词的“礼”的概念并不是孔子创制的,但是在他使用和讨论这个词的时候,却使它产生了远超乎被认为是较早一些时候出现的任何意义。
可以说,孔子给那种与“礼”相一致的行为附上了一种“魔力”功效。 [317] 关于孔子的宗教态度,无疑是个相当有难度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探讨。宗教仪式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孔子对于此类仪式并未表示过明确的怀疑,但是孔子在讨论与他的学说有关联的“礼”的时候,他通常是用非常理性的和常识性的社会心理学的词语来谈论的。我们一定记得,在孔子时代,社会的道德标准几乎全部崩溃。比如说,陈公和他的两位大臣同时与一个寡妇保持着公开的不正当关系,他们每个人都穿着她的一件内衣,还在公开场合拿这种勾当开玩笑。一位大臣发出抗议,对于公开暴露这种邪淫之事提出了批评,但这位大臣随后就被谋杀了。 [318]
在当时,只有在完整的宗教仪式中才能看到一种有始有终的行为范型(这种范型受社会所能接受的行为准则的规定),在其中,人的行动接受了共同一致的行动模式的促动,而不是被贪心和瞬间热情所操纵。因此,孔子才说,让这种模式发扬光大吧!孔子告诉弟子冉雍,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你的行为就应该好像是正在招待一位贵客”;假如你很幸运,能有一个管理人民的权威职位,就要十分小心地实践对你的信任,使你的行为“就好像正在帮助完成一场重大的祭祀一样”。 [319]
“礼”包含有礼仪实践的种种形式,但是只有这些形式是“内在的和精神的皈依表现为外在可见的表征”时,它们才是有价值的。确实,没有德行的人与“礼”是不相干的。 [320] 孔子说:“我实在不忍心去看那种由内心不虔敬的人所主持的礼仪。” [321] 他表示,在哀悼死者时,真诚的悲哀比小心翼翼地完成丧礼的每个细节更重要。 [322] 孔子非常反感那种纯粹的外在表现。他说:“礼啊,礼啊,难道仅仅是陈列上玉器和丝帛吗?” [323]
相反,真正符合“礼”的行为与平庸的循规蹈矩是不同的。后代的一篇文章说:“最伟大的尊敬不允许矫饰。”又说:“玉石的最高表征是质朴。” [324] 孔子则说:“礼,与其过分挥霍讲究,还不如失之于拘泥呢。” [325] 根据孔子的思想,如果我们不得不给“礼”下一个定义,那也许是“有品味的举止得体(good taste)”。
当然,所谓举止得体,是说做所有的事情都要恰如其分,这就是“礼”的要求。《礼记》陈述道:“礼是适宜的表现。任何行为都要以此为标准来做出妥当与否的判断,即使先王没有做过的。” [326] 这一点上,孔子的看法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说,按照“礼”的要求,参加祭祀时要戴麻冕(一种用麻织成的帽子,在当时比丝织的造价高)。孔子说:“麻冕是礼所规定的,但现在人们戴丝冕;丝冕更经济一些,所以我遵从大家的做法。”这样的改变只是因为太费钱。孔子认为,之所以说这种改变是可以接受的,是因为它只关乎礼的外在形式,并不违背礼的实质。但是,在下一句话里孔子强调说,为了妥当地完成“礼”所规定的整个仪式,有一种规矩是重要的,即宫廷礼节要求,臣下拜见国君时,在登上台阶之前要对君主鞠躬行礼,但是现在却逐渐省略了这种鞠躬。孔子说:“这是傲慢的表现,尽管与大家的做法相反,我还是认为,应该先在下面行鞠躬礼。” [327]
应该指出的是,这并不是卑躬屈膝式的阿谀巴结,绝对不是。孔子全面的看法是,臣民应该对君位表现出完全的和恰当的尊敬,但是,在接近君主本人并与他交谈时,人们应该实实在在地表现出他们绝对的信心,即使是这样做会被看作是冒犯。这才是礼! [328]
“礼”显然不仅仅是礼仪规则,所以,死板地固守这些规则,就会粗暴地亵渎真正的“礼”。然而,另一方面,完全用真情实感去表现“礼”也是不够的。礼是情感表露的运载工具,而这种表露一定得采取社会认可的方式。这是明显的要求。当今,某个地方以举起握紧的拳头表示友好欢迎,而换个地方便成了敌意的姿势。如果一个人承认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并以此身份去行事,那么,尽管他不需要被强迫,也必须遵守他周围的人所认可的惯例。所以,儒家意义上的“礼”的实践包含有一种知识:传统的社会实践加上调节它们的能力。这是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中生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常识。
对于个人来讲,“礼”的作用是要把人的行为导入社会所能接受的和对社会有用的渠道之中。“礼”把文明人同野蛮人区别开来,而野蛮人是要随时随地和不加约束地发泄其感情的。例如,对死亡的本能反应是失控的悲哀以及同时对尸体的厌嫌。对此,“礼”就可以提供一种调节手段,以便稳妥地对待和处理尸体,并以适当的符合礼仪的方式装饰之,以避免引起人的嫌恶之情。在丧葬习俗中,“礼”使人们能够利用一种可以接受的表现方式表达对死者的哀悼,同时还能减轻过度的悲哀。绝对不要让无节制的丧葬方式来削弱织成社会网络的家庭纽带,而是要让自己放弃疯狂的和无度的悲哀,因为这样的悲哀会破坏一个人和他周围人的生活。为了维护全社会的利益,“礼”为人们规定了一个采取适当手段来行事的进程。 [329]
“礼”实际上是平衡舵,目的就是防止不足或过度,把人们的言行导向对社会有益的中庸之道上来。因此,孔子认为:“如果没有礼的调节,殷勤周到就变成了徒劳费事;如果没有礼的调节,谨慎小心就变成了胆小怕事;如果没有礼的调节,勇敢无畏就变成了不守规矩;如果没有礼的调节,刚直坦率就完全变成了厚颜无耻。” [330]
“礼”作为指导和促进人际关系的方法是极其重要的,并且无疑是社会存在所不可缺少的。我们倾向于认为礼仪在朋友之间是碍事的,然而,过分随随便便地对待朋友也会毁掉友情。孔子说:“晏平仲很知道如何保持友情。尽管相识很久了,他仍是恭敬如初。” [331] 詹姆斯·F. 贝尔纳斯(James F. Byrnes)曾讲述过一个精彩的美国“礼”的例子。他写道,美国最高法院的“每一位法官,在进入直通法庭的会议室时,在场的法官都要握握手。当我最初成为其中的一员时,我有点认为这是很可笑的,因为我经常是只与一位或几位法官商谈定案。可是,我后来才得知,在许多年前一位大法官建立了这个惯例,其依据的理论是,无论前一天法官们有多么激烈的争论,如果他们以握手或几句寒暄语开始新的一天的话,就会弥合相互间的分歧”。 [332]
在教育方面,“礼”的重要性是明显的。既然孔子想让他的这些出身贫贱的弟子们做好在政府中发挥有效作用的准备,他就得教给他们在君子之间和在宫廷礼仪方面的礼节,这是“礼”的纯粹外在的层面。但是,过度强调行为修饰会使人成为单单是殷勤有礼的虚华之徒,死板地拘泥于形式而缺乏任何个人的活力,这是常有的一种危险。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后世儒学中是常见的。孔子完全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并做出过非常明确的警告。他要澄清的是,真正的“礼”与单纯的形式主义根本不同,因为“礼”是一种表现善良品质的方式,而不是对品质的隐匿或替代。孔子说:“构成君子品质的本质材料是义。君子是用礼来实现义的。” [333] 在另一个场合,孔子又说:“如果一个人的自然本性胜过了他的后天教养,他就是个没有修养的人;如果他的后天教养胜过了他的自然本性,他就仅仅是个受过教育的仆从。只有自然本性与训练所得和谐互补时,他才是个君子。” [334] 这就是说,“礼”并不是人格的基本品质,而是修养人格并使其表现善良的工具。 [335]
《论语》并没有明确显示孔子是否给学生们实际讲述过礼的运作,而弟子子夏后来则有过这方面的实际操作。 [336] 但是,无论孔子是否使用过这种已成惯例的身体姿态,他也显然认为,“礼”是约束情感的工具(这是被现代西方教育严重忽视了的人的一个方面)。孔子还坚持认为,有了“礼”所建立的平衡和节奏,个人就不会被任何危机震惊得做出令人遗憾的举动。这种附加在理智文化上的控制情感的功能被反复地加以强调:“夫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典籍,并且用礼约束他之所学,就不可能做出越轨之事。’” [337] 《论语》记载,在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有一次他们一行人陷入了窘境,以至于饿得很虚弱。子路愤愤不平地问孔子,君子忍受这样的磨难是否合适。孔子则告诉他:“也只有君子才能坚定地直面穷困。那些寻常之人,一旦处境不佳就站不稳脚跟了。” [338]
“礼”的概念意指生活中的某种和谐与礼貌以及个人的持守平衡。自从孔子时代以来,“礼”的作用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林语堂称它是“一种原则,已成为中华民族生活的目标,并且发挥着社会组织和管理的作用……” [339] 它造就了中国人民某些最卓越的性格特征。只是随着西方思想的流行替代了中国之道的地位,才使传统的“礼”的作用开始消失了。
孔子强调的另一项贵族式的艺术是音乐。许多重大的典礼都要有音乐伴奏。加上音乐有声乐方面的节奏与和谐,使得乐和礼经常结合在一起。中国人认为,音乐的教育价值并不仅仅(如我们西方人认为的那样)只能起到礼貌教养的作用。与中国人更为相像的是古希腊人的态度。在古希腊,“音乐的首要作用在于教育学方面,这种作用,在古代世界的意义里包含着品格与道德的确立”。 [340] 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具有塑造品格的力量,所以,在对年轻人的教育之中应该引入这一内容。” [341] 柏拉图则写道:“音乐训练是比其他东西更有力的工具,因为节奏与和谐能够找到进入灵魂的道路……” [342]
孔子对音乐深感兴趣。 [343] 《论语》有一章指出,孔子在一定程度上亲手校订过《诗》这部书, [344] 而这部书中的诗篇在古代是有音乐伴奏的。孔子会弹奏瑟,这是一种类似于(西方人在14—17世纪使用的)古琵琶的弦乐器。孔子也喜欢唱歌。 [345] 孔子与柏拉图一样,认为音乐不仅关乎个人,也关乎国家。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对于个人的思想品质,还是对于国家的道德风气来说,某一种音乐是有益的,而另一种则是有害的。所以,两位哲学家都认为,在理想的国度里,某些音乐应该鼓励,而另外一些应该取缔。 [346] 孟子引述孔子弟子子贡的话说:“听一听君王所赞许的音乐,就可以判断他的德行了。” [347]
我们不清楚孔子本人是否教授过音乐。从《论语》中纯粹偶然的提及中我们知道,孔子的两个学生(包括高大强健的子路)弹奏过瑟, [348] 所以,弟子们都会弹瑟也并非不可能。孔子确实与弟子们谈论过音乐,但他很可能希望他们最好是向其他教师学习,以期得到深造。他曾说,一个完人必须精通礼乐,以此作为对他的品格的最终修饰。 [349] 在另一场合孔子说,学生的品格应该“通过学习诗来激励,用学习礼来树立,用学习乐臻至完成”。 [350] 很清楚,孔子把礼和乐相联系。作为一位教师,这种观点不仅仅是理性的,而且是有感情和有灵性的。
现代西方音乐在技艺上无疑已经达到了音乐本身的最高的复杂性,但是,现代西方文化相对来讲并不太注意音乐的较深层的含义,这无疑会让人深感惊讶。事实上,自古以来人们就认识到,音乐会影响听众的情感甚至思想。可是,迄今为止,这种朴素的观点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进步。根据一项了不起的研究所得,音乐“影响着血压、心跳、呼吸、基础代谢和内分泌腺的特性”。 [351] 这项研究还认为,在某种条件下,音调对大脑皮层的波动产生了明确影响。 [352]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大量的有关音乐教育和音乐的道德意义的种种理论尚未被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对此主题却并没有人进行过真正的研究。然而,尽管人们不太留意音乐对“正常”人的影响,一些精神病学家有时却在研究(并运用实验手段)利用音乐治疗精神疾病。 [353]
我们不得不强调指出,孔子并不把“礼”和“乐”的技能看成是首要的。孔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学生们灌输的基本点是:信、信、信,讲求信用。孔子告诉他们:“如果一个人缺乏信用,就仅仅是没有套马横轭的马车,我不知有谁能够驾驭它。” [354] 当弟子子张请问“一个人应该如何行动”时,孔子告诉他说:“你的所有言语都要是诚实的和实在的,你的所有行动都要是体面的和谨慎的。如果能做到这些,即使独自一人处在野蛮人中间,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355] 孔子称赞过两种人:一种人非常谦逊,不羞于向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寻找启迪;另一种非常正直,能把有功劳的下级提拔到与他们本人相等的地位。 [356] 孔子也藐视虚伪,使他深感羞耻的是那些有意降低身份的“机巧的谈话、虚假俗气的外表和做作的尊敬”。 [357] 他明确宣布,那些用严苛专横的样子掩饰内在不足的人,至多不过是个盗贼罢了。 [358]
然而,单纯的守信(这是值得钦佩的和必须的)也还是不够的,完全不讲究具体条件的诚信就等于犯了错误。孔子告诉弟子们,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一个人应该无论如何都要下决心去证实他的话语,无论境况怎样都要完成已经开始做的任何事情,但这并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行为。 [359] 他说,君子虽然会犯种种错误,但他们一定得随时准备改正自己的错误。 [360]
进而言之,孔子告诉他们,仅仅在思想和言论上做到守信是不够的,真正的守信要落实在行动中。从政者首先应该尽心竭力地完成政务,而把俸禄和其他奖赏放在次要的位置上。 [361] 如果认为是正确的就不要怯懦,而是要大胆地去做。 [362] 如果有必要,一个人应该为了原则而放弃他的生命。 [363]
为了鼓励这种行为,孔子着力使用了一种方法,即在学生面前展示“士”的理想。“士”这个字的原意可能仅指一个年轻人, [364] 它也渐渐意指“兵士”,以及(依照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普通演变的过程)“贵族”。在此意义上,“士”极有似于欧洲人所说的“骑士(knight)”。这两个词均指一些最低层的贵族,通常是军人。但是,孔子在此又一次做出努力,给与“士”这个词以不同的意义。在过了一千多年后的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会才担负起了“驯服无节制的和野蛮的武士阶层的任务”, [365] 并努力使用了种种办法,相当成功地使骑士们信奉了教会的道德和事业。孔子所做的在一定程度上与欧洲的情形有些相似。孔子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只有像真正的君子那样,才配称作“士”。同时,任何以儒家德行为典范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就是最高意义上的“士”。
基督教会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了传统骑士式的优点,即勇敢、忠诚和奉献精神,鼓动这些年轻的贵族发誓“竭尽全力保护弱者、寡妇和孤儿”,并把他们好战的能量发泄在十字军的圣战中。孔子所说的“士”也可能暗示了真正的士人被期望具有的热情和奉献精神。他说:“只想着平安地待在家里的士是不值得被看作士的。” [366] 弟子曾参说:“士一定要有气魄宏大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勇气。因为他的责任是沉重的,而完成责任的道路是漫长的。完美的德行是他所担负的责任,这难道不是沉重的吗?他的奋斗路程只有到死才是终点,这难道不是漫长的吗?” [367]
可是,必须强调的是,基督教的骑士其实仍是骑士,仍然是贵族的一员,而儒家的“君子”一般来讲根本不是武士,通常情况下他们甚至不是世袭贵族。孔子尽力给弟子们灌输的是贵族阶层的德行而不是其缺点,他也只是借用贵族的声望而并不教授弟子们如何行军作战。从终极意义上看,孔子的这个意图取得了成功,以至于纯粹的武士不再能与受中国人尊敬的学者一争高下。
孔子使其弟子们感觉到他们从事的是最高尚的职业,就孔子能够展示给他们的而言,这个职业的报酬只有内在的平静和精神的纯化。这种内在所得来之于以下的保证,即一个人要尽力去做高于其他一切的真正有益的事情,而最终成功与否并不重要。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责任显然是纷繁而又沉重的。
孔子不断向弟子们强调修身的重要性,这份责任必须由他们自己来承当。如果他们有了任何进步,有时尽管很小,功劳也是自己的;如果他们突然停在目的地的前面,即使是很近,他们也一定得自己担负失败的耻辱。 [368] 孔子要他们牢记,“即使一支大军的将帅也可能被绑去,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夺取甚至是一个最卑贱之人的决心”。 [369] 自信和独立也是特别受人欢迎的话题。“君子在自己的内部求索,小人则向别人提出要求。” [370] “不要担心没有官位,而是要担心对官位能否胜任;不要担心你不被人知用,而是要担心是否名副其实。” [371]
人们当然应该批评任何形式的道德缺陷,但要批评他们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 [372] “一个人应该严于律己,但对别人却要宽容,以免引起怨恨。” [373] 孔子说:“即使仅仅与两个人同行时,我也总是向他们学习。我选择他们的长处去效仿,对他们的不良之处则要避免。” [374] “当你看到一位可敬之人时,要想着努力赶上他;当你看到一个不怎么样的人时,就要向内审察你自己(是否也有那样的毛病)。” [375]
孔子期望弟子们成为谦逊的人,当他们做不到时,就会受到孔子的挖苦。孔子告诉他们说:“孟之反这个人不是自夸者。当军队被击溃时,他最后逃生。但当他接近城门时,却一边鞭打着他的坐骑一边说:‘不是我的勇气使我殿后,是我的马不往前跑。’” [376] 孔子说:“君子羞于让他的言语超出他的行动。”ᣪᣳ [377] “他先去行动,而后再去谈论。” [378]
使孔子大皱其眉的不仅是自吹自擂,而且还有任何形式的过分健谈。孔子充分认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以及它在比如外交活动中的关键作用。 [379] 但他认为,在某种特定情势下,言语应该是简明扼要、直截了当和便于使用的。孔子说:“言语只要能充分表达说话者的意思就行了。” [380] 他认为喋喋不休是可耻的。孔子告诉学生们,如果一从其他人那里听到了什么,马上就向别人重复,(而没有自己进行思考)他们就会一无所获。 [381] 孔子说:“君子嘴钝。” [382]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孔子认为,言语善辩之人近乎让人憎恶。在他讲给颜回的许多伟大原则之中,以下要求是适合于治理政府的,即“远离机巧的谈话者,因为他们是危险的”。 [383]
这种对善辩之人的嫌恶看上去有些过分甚至很荒唐,但事实上却有着正当理由。根据有关记载,孔子并不是努力用述诸最后权威的要求或呼吁来说服这种人,相反,孔子要尽力以理服人,用善辩之人的喜好辩论的长处来进行讨论。但是,无论何时何地,一旦善辩之人和狡辩之言辞加入进来,真正的论证就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善辩者的目的不是寻求真理而是赢得口舌上的胜利,而为了这个目的,他们经常是尽可能地远离真正的论题。辩才和辩论的用意不是解决论题,而是操纵人们。为此,善辩之人非常倚重发泄情感和表达先人之见,以及利用灵巧、机智,有时是幽默来转移话题,而不是深入分析思想内涵。不用说,孔子瞧不起所有的这一切。
辩才是政治领域里非常危险的人物。在民主社会,他们会把人民导入歧途;在君主集权社会,他们又要不择手段地实现操纵君主的目的。而孔子则哀叹道,在他那个时代,一个没有善辩之能的人要想躲避灾祸将是非常困难的。 [384]
正如我们在上文已经见到过的,阴谋活动是那个时代的家常便饭。孔子断言:“我痛恨看到使用利口颠覆国家和家族。” [385] 尽管这种阴谋家可能在短时期里慷慨奖赏儒家集群,可它最终会使儒家的活动名誉扫地。孔子足够精明地认识到:“一个不断寻求小利的人从未办成过大事。” [386] 他自己尽量避开政治阴谋,也教导弟子们依靠礼貌、诚实和守信使他们的事业受人欢迎,而且要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机巧之言辞。这都是孔子的光荣。 [387] 孔子对于这种思想的坚持可能是导致以下结果的原因之一,这种结果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与许多国家相比较而言,讲演术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
既然儒者是负有使命的人,孔子就有责任保持举止的尊严,以便不损害他自己和集群中的人们的荣誉。 [388] 孔子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当中,并为此而深感自豪,根本没有必要跟别人去争辩。 [389] 孔子并未寻求速成,而是在深思熟虑之后采取行动。这种深思熟虑使他自己充分弄清了合适的行动路径。 [390]
以自私为动机的行动有损于孔子的尊严。“君子吃食时并不求得餍饱,他的住处也不求得安逸。” [391] 君子关切的是义,而把获利的动机留给小人。 [392] 即使是荣誉(特别是以卑劣手段得到的),与自尊相比,对君子来讲也是无足轻重的。 [393] 子贡问道:“一个人如果被所有的同乡之人所喜欢,您说这人怎么样呢?”孔子告诉他:“这说明不了什么的。”“那么,全乡之人都不喜欢的人又怎样呢?”“这还是不足以给他下断语。最好是他被好人所喜欢,而被坏人所憎恶。” [394] 然而,尽管他蔑视的仅仅是虚名,孔子还是认为,君子并不愿意一生之中了无所成,以至于刚一死去就被人忘掉了。 [395]
孔子展示给他的学生的真君子的理想也许可以概括为某种精神的高尚性,而不是高傲性。孔子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是被卑劣、贪欲和暴力所包围的,所以,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已经认识到非常有必要(在理智上)从他们的环境中退却。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非常困难的。当我们体谅他们在如此退却的同时仍须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并且不得不参与它的政治事务的时候,体谅这种退却既没有形而上学的根据又没有宗教的实质性的援助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它是人类精神的主要成就之一。
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是自豪的而不是妄自尊大的。 [396] 他们是易于侍奉的,因为他们期望与之共事的只是那些称职的人;但是,他们也是难于取悦的,因为他们不喜欢那种有意取悦他们而又与最高原则相悖而行的人。 [397] 一般来讲,与孔子本人共事并不难,同时孔子也是容易相处之人,他并不是一个党派性很强的人,也不想建立任何派系。 [398] 因为孔子的品格是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所以他在直面非常时期时也能镇定自若。 [399] 虽然他从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会在何时被折磨至终,但他并不惧怕:“夫子说:‘内省之时,如果发现自己并无欠妥之处,为什么要忧愁,有什么要惧怕呢?’” [400]
所有这些听起来很像是干巴巴的说教,然而,孔子并没有错误地认为人们仅凭斯语即可为善。其实,正如《论语》之中的孔子反复强调的,更重要的是榜样的力量。他相信一种真实的“品格传播”。孔子说,某位鲁国人“确实是个君子之人。如果鲁国没有真正的君子,他又是如何获得这种品格的呢?” [401] 孔子严肃地告诫他的弟子们要高度重视他们的交往之道。正如工匠必须磨快工具以便做好工作一样,弟子们也必须依靠以下两点使自己的品质有所进展,这就是:只与贤明的上司共事,只与有德之人建立友谊。 [402] 孔子说,一个人应该善待所有的人,但却只与那些真正的有德者相亲近。 [403] 他再三警告,不要怀着错误的忠诚意识与下面这种人建立友谊:他们的行为没有价值,还拒绝加以改变。 [404]
孔子自己的典范力量在他的学说中无疑发挥着首要作用。他的不拘泥于形式的性格以及他与弟子们的亲密无间增强了这种力量。事实上,没有什么例子能够说明孔子言而不行。他有两次被邀与反叛者结盟而遭到子路的反对,但他最终并未入盟,尽管他认为有理由为自己的冲动作辩护。 [405] 毫无疑问,孔子有责任向那些受他的决定所影响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没有例外的榜样。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直到此时,不管是孔子,还是我们的分析,几乎没有提及什么书籍,特别是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儒者”这个词被看成几乎是书呆子、蛀书虫的同义词时,这样无视书本就会更让人感到诧异。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在孔子去世后的几百年中,儒者逐渐变得太专注于书本了。到后来,政府推行的科举考试以及对儒生的教育都变得过分书本气,以至于宋朝的改革家王安石在1058年抱怨道,他那个时代的教育主要是“对古典原文的注释、字斟句酌的分析”。他接着评论道,这“不是古代的(教育)方法”。 [406]
这确实不是孔子之教的方法。孔子把对文献的研究看作是君子教育的一部分,但也只是一部分。更基本的是品质的修养,以及学会与(作为社会存在的)亲戚和同胞一起生活。 [407] 想去学习书本的内容固然很好,但是对书中所言要有真正的理解,或者是要把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孔子坚持认为,如果没有行动,仅仅记诵书本的内容是无用的。 [408] 《论语》有一章说,“夫子教授四样东西”。确实,如何译出这四样所代表的东西的特质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个难题。它们也许指的是“文献、行动、忠诚和良好的信用”。 [409] 无论如何,它们所暗示的是,书本只是全部必修课的一个方面。
《论语》唯一经常提到的书是《诗经》,孔子仅仅称它为“诗”。这是一本诗集,它的各种类型的诗是由各种各样的作者写下的,并集成于周朝初年到西元前600年之间。现存《诗经》有311首诗。孔子指出,他知道的这本书大概有300首诗。 [410] 这与现存的差不多,但也不完全一致。 [411] 我们将把孔子是否写过或编订过这本书和其他书的问题留待下一章讨论。在此,我们只谈一谈孔子把它们运用到他的学说中的问题。
孔子告诉儿子伯鱼说,如果不学习《诗》,就“好像是一个面墙而立的人”。 [412] 有一次,他对一群弟子说:“我的孩子们啊,为什么不去学习《诗》呢?《诗》会激发你们的情感,使你们具有更加敏锐的观察力,还可以扩充你们的同情心,并缓和你们对不公正事情的不满情绪。在家中,它对侍奉父母是有用的。在外面,它对你们事奉君主也是有用的。再往远说,它还会使你们多熟悉一些鸟、兽、花草和树木的名称。” [413]
所有这些都是相当真实的和可以理解的。可是,诗篇在古代中国那个时候的另一项用处就不那么简单了。诗篇被认为(至少在多数情形中是相当程度地被曲解了的)有隐含的比喻意义。这样一来,这个隐喻之意就被外交官用在他们的外交辞令中了。因此,在盟会或宴会上,两个或更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展开他们的论辩并以一种朦胧的方式立论,这就是引用包含有(或被认为是包含有)隐意的诗句。他们的对手将被预想为是能够知道这些引语并能立刻理解其蕴意的。如果可能的话,对手就得引述更恰当的诗句作答,以期驳倒对方的论点。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被认为是输了。 [414] 因此,对《诗》的熟知是一个人梦想进入高层官僚圈子的基础。孔子与他儿子的另一次谈话可能就是针对了对《诗》的如此使用。孔子说:“如果你不学习《诗》,在讲话时就没有什么可资使用的。” [415] 但他又说:“一个人可能会背诵所有的三百篇《诗》,但是,如果他处理公务时没有效率,派去执行外交使命时又不能做出独立(亦即不用助手的提示而使用诗句)的回答,尽管他很博学,又有什么用处呢?” [416]
当我们进行讲演时,也会经常引经据典,这与上述情形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但我们在进行这样的引用时要非常慎重,并且认为对引语原意的过度曲解是一种缺憾。可是,在《诗》的正统解释中,注释者总是无视诗句的明显意图,而是经常地更看重他们自己对诗句的理解。这一结论,是许多当代中西学者的观点。 [417]
例如,有一首叫作“鸡鸣” [418] 的诗,诗的内容很清楚,是一场对话,对话的双方是一位年轻女子和她的情人,地点是这位女子的卧房。她告诉他鸡已打鸣,黎明到了。但他说不是鸡鸣而是苍蝇的嗡嗡声,不是天亮而是月亮正在升起,所以最好还是甜甜地再睡上一觉。但此时她对他已忍无可忍,告诉他赶快回家,以免她为此而恨他。可是,正统的解释却说是一位“贤妻”督促她懒惰的丈夫起床上早朝。
在我们所能拥有的有关孔子的任何材料中,孔子并未犯过如此荒谬的理解诗句的过失,但是,孔子也曾有两次用类似的方式与弟子讨论诗句,并且离开诗句的本意也是相当之远的。 [419] 我们可能得接受顾颉刚的看法。顾氏认为,由于孔子自己这样使用过诗篇,他就应该对后世儒者过分富于想象力地理解和使用诗句负有很大的责任。 [420]
没有证据表明孔子对书本有过任何例行的讲习,或对弟子们的学习书本有过系统的指导。通常的教学之道是,孔子告诉他们研究某个主题,然后与他们就此进行讨论。就《诗》而言,他只是推荐给弟子们学习。但是,在他倡导学习音乐的时候是否也指定过一本书,这就的确是个难题了。一些学者认为,在音乐方面有过一本古书,而另一些人则否定之。无论如何,并没有孔子使用过这样一本书的明证。
关于礼,某种程度上讲我们遇到了同样的情势。虽然在“十三经”中有三本礼书,但令人怀疑的是,它们中的任何一本在孔子的时代是否以现在的形式存在过。其中的两本,即《周礼》和《礼记》,很明显是晚出的。 [421] 第三本,即《仪礼》,其中至少有一部分的内容稍早于其他两本,但其日期却难以确定。某些传统的观点把它的日期早早的定在周朝初年,另一些人则认为其中包含了孔子关于礼的学说。 [422]
不过,有关礼的某些文本最起码在孔子之后的年代里有过一定程度的校订和增补,这种看法大抵是可以成立的。因此,我们就不能对有关“礼”的任何文本做出保证,不能说某本“礼”书确实曾以现在的形式存在于孔子时代。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这些书写的是礼,某种类型的礼。 [423] 所以,当孔子告诉弟子们学习“礼”的时候,他很可能是指示他们应去阅读某些文献,并且去实践它们所阐述的观念。但是,孔子当时所指的到底是哪些文献,我们却不得而知了。
最后,《论语》提到了所谓《书》的文献。“书”从字面上讲指的就是文献、文件,但它逐渐用来特指政府的文献,这样的文献会保存在类似现在的档案馆的地方。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文献产生的时代,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直到稍晚于孔子之时,这些文献中的一部分才被编辑成集,成为我们熟知的《尚书》。 [424] 因此,当孔子在《论语》中说“书曰”(一般译作“《尚书》说”)时,事实上可能仅仅意指“有一种文献上说”。
《尚书》是“五经”之一,是最早的一部儒家经典。然而,我们在《论语》中没有看到多少书的证据。只有三条。 [425] 但这三条所讲的也不是孔子让他的学生们去学习这些文献的训诫。
综上所述,在孔子本人的学说中,书本的地位是相对弱一些的,这与后代儒家人物的实际做法形成了鲜明的不同。而且,正是在后世儒学的发展中,才使“儒者”和“文人”成为同义词。当我们审察孔子之后的儒学历史时,将会看到对书本之强调的日渐加强。这是个意义重大的象征,它表明儒家人物的兴趣已经与实际的社会改革相疏离,并转变到了更专心于抽象学术的方向上去了。
第八章 学者
孔子说:“学习,并在时机到来时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这难道不是很令人满足的吗?” [426] 《论语》开头的这句名言,立刻告诉我们孔子是位学者,而且他的学术目标是实践性的。
孔子是好奇的。对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孔子都要提出种种疑问,而并不在乎这是否会使他蒙受无知的名声。 [427] 尽管不能说他总是尽量小心翼翼地用最科学的标准去定夺是与非,但孔子却是在倡导一种合理的态度,即对于所获材料和依据予以批评性的鉴别。孔子劝告一位弟子去实践,但“对有疑虑的东西不要轻易下判断”。 [428] 他为誊抄书籍者感到惋惜,这些人在誊抄时不是在他们不能确定原文中的某个字的时候留下空白,而是凭猜测填空。 [429] 孔子说:“喜好智慧而不喜好学习,会导致一知半解式的概括总结。”这个表述可以说是很好地道出了实质性的问题。 [430]
用孔子自己的说法来讲,他15岁时“就开始学习”。 [432] 尽管他在大多方面是非常谦逊的,但他还是公开承认他比大多数人更为“好学”, [432] 而其他人也同意孔子的这种自我鉴定。在他自己的时代和他以后的时代,孔子都被看作是格外勤勉之人。实际上,在他死后很久写成的种种著作中,与孔子有关的传统说法的发展使他逐渐有了超自然的智慧,并且还把他描绘成一个精通各种古代知识和奇异学问的人。据说,无论什么时候,即使是在其他国家,人们只要发现了不同寻常的东西,都会去请求孔子加以解释,而孔子也往往能够做出令时人满意的解释。 [433] 这是传奇,而传奇通常会歪曲对实情的洞识。实际情况则正如这些故事所认为的,孔子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学问的人。
可是,孔子教诲弟子时并不把书本作为主要方面。当他讲到学习之时,并不是仅仅谈及读书, [434] 品格的修养也在“学习”这个大标题之下。然而,孔子确实学习过书本。对这一点,我们不仅有《论语》的证明,甚至总是在毁谤孔子的墨子,也勉强认为孔子“对《诗》和历史文献有广博的知识,并能明晰地理解礼和乐”。 [435]
每个人都认为孔子研究过书本。但是,当我们来问,他是否也写过书,或者至少是否编辑过书本时,大家就会处在论战之中。这种论战尽管一直在进行,但至今也未能弥合中国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在这个问题上,康有为的理论可能是最极端的和最具有党派性的观点。康有为(1927年去世)这位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和改革家,断言孔子是位多产的作者。1897年,康有为出版了一部书,名叫《改革家的孔子》(《孔子改制考》)。该书坚持认为,孔子的确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彻底改变。康氏宣称,孔子为了使自己的改革理论顺理成章,就把他的所有创制都说成是古制的复兴。在康氏看来,尽管这样的说法并不是真实的,但其动机却是正当的,正如慈母用鬼怪故事让她的孩子们感到快活也是正当的一样。 [436] 根据康氏所说,孔子为了使自己编撰的故事更可信,就撰写了所有早期经典。换句话说,孔子编写了所有的古代文献,而其中的一些文献从早于他的生活时代就开始流传了。 [437]
为了支持这一主张,康有为不仅引用了大量汉代(这太晚了,不足凭信)的证据,而且也使用了较早的著作。可想而知,这些证据肯定是最软弱无力的。在有关的论证中,康有为的第一个“证明”多少具有典型性。康氏引用了墨子的说法:儒者反复引用《诗》。于是,康氏宣称这“最清楚”地说明了是孔子编撰了《诗》。 [438] 当然,我们仅从这种证据中很难理解康氏为什么那样热烈地信仰他的理论。但是,只要看一眼他所从事的事业,就会明白一些的。康有为是当时中国学者小集群中的一员,这些学者认识到,在19世纪末叶,中国必须采用许多西方的技术,否则就会被列强蚕食掉。然而,他们的进行现代化的企图被保守主义所阻挠,而同样的保守主义又迫使康氏在1898年逃亡日本。在当时,阻挠他们的核心力量就是正统的儒学。所以,正是这个事实才剧烈地(尽管无疑是相当真诚地)促动了康有为,使得他在1897年尽力让以下思想得以普及,那就是:孔子自己与过去决裂了。所以说,康氏试图建立一个违背先例的先例。
发生在中国近代的这个事件与我们的探究并无直接关联。但它是一个理想例证,证明有人使用了以下方法,即:孔子和他的著作一再成为政治和政策的玩物,直到实情变得模糊不清。它也清楚地指明,我们必须抛开学者和政治家们所有的争论,并回到早期材料之中,以便弄清楚孔子是否撰写过什么著作。
《论语》中只有一章可以视为从总体上回应了这个问题。在相当含糊的上下文中,孔子自认为“是个传递者而不是制作者,相信并热爱古代”。 [439] 这通常被认为是孔子否定了他写过任何东西。但是,既然我们不知道孔子讲这话时的语境,或者讲这话的时间,它就证明不了多少东西。
《史记》认为,《诗》起初有3000篇,但孔子对它进行了删减,挑选了最好的305篇留了下来,成为后世的《诗经》。 [440] 我们必须留神这个记述,因为《史记》述及孔子的地方并不总是可信的。古今的学者都对孔子删节《诗经》篇幅的说法提出了疑问,他们指出,(早于孔子的)早期文献所引用的诗句中,并没有多少是在这个集子之外的。 [441] 孔子两次讲到了已经成为一个集子的“诗三百”。 [442] 如果他曾删定过它的篇数,这种删除将是相当随心所欲的做法。而且,孔子还引过一首不在现存《诗经》中的诗, [443] 并且两次责怪(有一次称它们是放荡的)一整部分诗,这些诗是在现存的三百首之内的。 [444] 如果他整理过这部书,这就是很奇怪的说法了。
可是,孔子确实说过,他从卫国返回鲁国后确定了“诗”的类别,“使它们得到了合适的位置”。 [445] 这意味着他做了某种程度的重新安排篇目的工作,但是,这可能是他在《诗》上面做到极致的工作了。
有一些相似的故事产生了以下结果,即认为孔子编定了《尚书》,或者是从3240件原始文献中挑选了若干篇组成一本书,还为它写了序言,这篇序言出现在后来各种各样的著作中。 [446] 然而,去审察这些内容纯属浪费时间。正如上一章所述,在孔子时代,合这种政府文献为一处的集子的确是没有的。如果孔子编辑过这样一个文献集的话,那么,在一个世纪之后,孟子就很难对《书》的篇章说出这样的话:“与其完全相信它们,还不如压根儿就没有它们”。 [447]
《春秋》也被认为是由孔子编著而成的。不过,这种看法并不会马上就能用简单的推论驳倒。《春秋》是一本简要的和未加修饰的编年史书,记载了西元前722—前479年间鲁国发生的事件。这部书只是关于政治事件、国家联盟、重要人物死亡以及发生战争之日期的一付干巴巴的骨架。它偶尔也记载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诸如“这年春天没有冰冻”、“椋鸟来到,在树上筑巢”,以及“六只鱼鹰倒着飞过宋国都城”。 [448] 显而易见,这只是一部记载一些孤立事件的编年史,其中的内容是由宫廷史官记载下的已经发生了的或变得知名了的事件。 [449] 如果不是因为《孟子》某些章节的说法,可能不会有人老是认为它还会是别的什么。
根据《孟子》的说法,孔子写过一部叫作《春秋》的书,而且,此书完成之后,“叛乱的大臣和坏分子都被恐惧所震慑”。 [450] 然而,在我们读到的《春秋》中,并没有什么地方明显地有意制造任何这样的效果。可是,后来的儒家学者却把书中的某些事实汇集一处,认定这本书一定有“隐义(微言大义)”。结果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日没夜地辛劳,目的就是要破译《春秋》所记载的整个历史中的密码,但是,这可能是一个极其过分的企图。比如,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所得,在这本书的记事中,对于各种人物的死亡的表达上使用了明显不同的词语,以表示对这些人物生前行为的“称赞或谴责(褒和贬)”。可是,这种原则未被发现可以运用于全书。同一个解释者,在此处把某句话描述为谴责性的,而在彼处又解释为赞誉性的。 [451] 用冗长的篇幅研究这些意图的理雅格(1815—1897)写道:“整部书就是个谜语集,对这些谜语,有多少个解谜者就有多少个谜底。” [452] 如果真有一个密码,这些有意图的努力应该会解开它。但事实证明,这毕竟只是一部简约的编年史书。
那么,孟子的话证明了什么呢?答案是,孟子所说的《春秋》(根据孟子的表述,是孔子所作)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春秋》。在古代中国,有多种史书都用这个书名,而孟子的描述,在好几个方面都不适合我们现在的这部书。 [453] 实际上,孔子究竟是否写过任何叫作《春秋》的著作是非常令人生疑的。孟子说,孔子认为他自己写这部书的首要目的是扬名; [454]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为什么《论语》却没有一个字提及孔子曾写过这部书或任何别的书呢?有一个不能视而不见的事实是:在孟子时代,儒家传奇大量涌现,以至于孟子本人就认为有必要解释为什么孔子没有成为天子。 [455]
孔子也被认为是“礼”之本源。在有些人看来,即便孔子没有亲手撰写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最早的“礼”书——《礼记》的任何一部分,这部书的写作也要归功于他的启迪。 [456] 这种说法是很令人怀疑的。但也有证据表明,孔子所做的大量努力确实刺激了人们对“礼”的兴趣,所以,他至少是间接地鼓励了人们就此论题进行写作。《论语》不仅证明了孔子对“礼”感兴趣,而且还指出他对“礼”进行了历史的考究。在这本书中,甚至有人还认为孔子能预测“礼”在未来的变化形式。 [457] 可是,并没有早期的材料为《史记》的断言作佐证,这个断言说的是,孔子“整理”了《礼》。 [458] 《史记》的这种说法意味着,孔子要么是撰写了要么是编辑了一部有关“礼”的方面的著作。
同样的论断适用于“乐”的情形。孔子对“乐”很感兴趣,并去研究它,但没有证据说明他曾写过有关它的任何东西。 [459] 我们甚至不能肯定在早期中国有过一部音乐专著。
在有关孔子是否撰写过什么著作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考虑的最后一本书是《易》(变易之书,《周易》)。它实际上是一本算命占卜者的手册,据说如果学会使用它,就可以用它来预测未来。这部书包含了两个相当不同的部分,即原初的文本(《易经》)和一系列附录(《易传》或“十翼”)。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原初文本的产生时代早于孔子,但顽固的传统说法却把附录的著作权给了孔子。甚至在当今都还有一些有鉴赏力的学者仍相信孔子写作或编辑了附录的某些篇章或全部附录,并根据对这些附录的分析来讨论孔子哲学。
可是,一些最有鉴赏力的学者们现在认为,孔子与《易》的产生毫无关系,这是一种正确的观点。对此,我们拥有大量的证据。到了孔子时代,尽管占卦问卜在中国已经有了至少一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历史, [460] 并且孔子时代的人们也经常使用它,但是,并没有早期资料说明孔子曾经使用过占卜。实际上,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孔子和早期儒家对于占卜是大皱其眉的。
可是,《易》在后来却引起了一些儒家学者的注意,他们对这本书进行了热情的研究,以至于逐渐把它列为“五经”之首。然而,正是这些后儒制作了《易》的附录部分(即“十翼”),并把著作权归于孔子。可是,孔子事实上不仅根本没有使用过占卜,而且从未提到过这本使人不安的《易》。《论语·述而第七》中的一章被认为与《易》有关,但这是被改动或插入的,以便让孔子明确认可人们对此书的研究。 [461] 当我们渐次去审察后代儒学(我们将考虑这种发展的某些细节)时,完备的证据将会展现出来(原书第198—202页)。这些证据非常清楚地说明,孔子既没有撰写过又没有编辑过《易》的任何部分。
完成了对那些被认为是孔子所著之书的审察之后,我们的结论是,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能说明孔子曾写作过或编辑过任何一本书。这并不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断言,越来越多的学者近年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462]
孔子没写作这些书,他也就至多是读一读它们并把它们运用在他的教学中。这就有必要探究它们在与孔子思想的关联中所起的作用了。为有助于我们给这个问题寻找答案,让我们审视一下孔子引用这些书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记载于《论语》之中。
在《论语》中,《诗》的引用要多于其他书。孔子直接引用或间接提到《诗》(或“诗”)共有7次。其中的3次是直接引用原诗,并且没有曲解其原意。 [463] 但其余的4次却没有使用其本义,而是把诗句的原意进行了曲解、牵强附会或完全改变。 [464] 最突出的一例是,有一行诗的意思被孔子引用为“让你的思想中没有邪恶(思无邪)”。 [465] 这些字句所表达的思想在《论语》此处的上下文中是可以的。但是,正如韦利指出的,被意译成“思想”的“思”字,在原诗中只表示感叹,相当于感叹词“啊”。这首诗讲的是养育马匹,而这一行的意思是:“啊,(让马)平安无事吧!” [466]
由某种文献逐渐结集而成的《书》只被《论语》引用过两次,而出自孔子之口的则只有一次。 [467] 这多少有些让人惊讶,因为习惯上认为孔子从这样的书中汲取了思想。在其中的一个场合,孔子甚至说:“有文献上(“书云”)。”实际上,孔子是把他引述的章节牵强附会,以适合他自己的目的。 [468]
我们无法确定孔子对于那些讲述“礼”的文章知晓多少。在《论语》中,孔子是否引用了这样的文章也从来都是不清楚的。他也从未说过“《礼》曰”之类的话。《仪礼》中简短的一节以及《礼记》中零散的四句话与《论语》的几章相同或非常相似。 [469] 但很有可能的是,正是有关“礼”的那些书引用了《论语》(或者是儒家的思想传统就是建立在《论语》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相反。
在孔子引用的一段文字中,有8个汉字显然是《周易》上的话。在以下引文中,我们用不同的字体标出这8个字。“夫子说:‘南方之人有一种说法:一个不能持之以恒的人甚至都成不了一个好的巫师或医生。这话说得好啊!“(如果)他的德行是易变的,他就有可能招致耻辱(“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所以说,)仅仅去占卜是无效的。’” [470] 这是孔子在《论语》中唯一的一次提到占卜。有必要指出,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孔子是非常不相信预言的。
孔子读过的书比《论语》中直接引用的书籍的总和无疑要多得多。孔子把他的读书之所得融合为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首尾一贯的思想体系。孔子不是那种学者,说出的言辞完全由引语拼凑而成。在与他人进行的思想讨论中,孔子并不依靠已有的权威著作支持他的主张。他更感兴趣的是一种主张是否合理,而不管它是否能在书本中找到根据。孔子的独创性弥漫在那样广大的范围之中,以至于他通常是以自己的一定之规来引述书本上的话,而对于这些引语的本来意义却不甚留意。
孔子并非起初就想做个学者,也不是最初就有意要去做一个教师。孔子看到了他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充满了灾难,所以,他的主导思想是要把这样一个世界改变成福地。为了将此项工作进行到底,孔子使用了许多工具,其中就有书本,但他的兴趣并不是为知识而知识。当一位弟子请求教授农活儿时,孔子指出这不值得君子去学。 [471] 孔子认为,他的世界的当务之急集中在与道德和政治相关联的各个领域,而他就把他的教学和研究朝向了这些主题。孔子毫不隐讳地痛惜那种不能转化为实际用途的博学, [472] 这不是说做学问本身是一件坏事,而是因为它是当时社会现实所消费不起的奢侈品。
第九章 哲学家
从古至今,出现过数目大得惊人的论述孔子思想的著作。可能没有其他哲学家能得到比孔子更多的讨论了。然而,我们可以依赖的关于孔子哲学的知识却是令人遗憾地贫乏。这其中有几个原因。不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孔子的思想类型是一种稍现即逝、极其难以把握的现象。实际上,它几乎是必然如此的。
在人类历史上,孔子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许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固守着旧的宗教信仰与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模式。但是,在西周封建政治模式逐渐被打破时,其他领域都受到了影响。长期把人们束缚在一起的绳索被抛弃了,给个人带来了相对的自由,而社会则近乎混乱一片。与此极其相似的一次危机也出现在了大约西元前2100年的古埃及。 [473] 而在古希腊发生的某些事情亦可在此作一比较。正如温德尔班德(Windelband)所描述的:“个性的过度发展越要松弛公众意识、信仰、道德的旧的束缚,无政府的危险越是危及新生的希腊文明,那些因生活地位、思想和性格而出众的人物就越会感受到拯救即将殒灭的他们心目中的生活准则的紧迫性。” [474] 在希腊,这样的社会状况给了我们苏格拉底哲学;在中国,则是给了我们孔子哲学。
在这种道德和政治危机的时代,人们倒退到了他们基本的人的属性的水平。仅仅去祈求旧的神灵和引用旧的权威再也不够了,因为他们都是令人生疑的。要紧的是开始认真考虑基本原理,并去处理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事情。那些在这种时代敢于做先驱的人们不会轻易地使他们的思想为人们所接受。他们需要不断地与怀疑论者的批评进行斗争,以保持他们的哲学的倾向性和坚定性。
这种哲学有一个普遍的特征。它们可能使用一些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的词汇。孔子可以把“天”说成是他的使命的保证人,苏格拉底把“美”称作是本身与美的对象相分离的存在物。 [475] 我们可能不会接受这些观点。然而,尽管有时代和文化的不同,他们却都讲述着我们的语言。我们觉得他们正在处理着一些真正的问题,而他们之所说都对问题的解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这种哲学不可能是持久不变的。如果它们成功了,那么,它们的真正成功导致了对它们的滥用。那些继承它们的人对它们的概念的阐释远远超出了它们原初的形式。危机过去了,社会安定了。新机制取代了旧机制,哲学与现存秩序达到了一致。根据约翰·威尔逊(John A. Wilson)的看法,在古埃及,伴随着古王国崩溃之后出现的危机,带来了中王国治下的“社会——道德进步”,而这种进步,又在帝国(Empire)的治下逐渐消失了。这样一来,较早的个人主义被一种“人的无助意识”所代替,并且变成了“全体一致的和形式主义的”模式。 [476] 由柏拉图作了详尽阐述的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最终产生了普洛蒂诺斯(Plotinus)和波尔费里(Porphyry)的复杂而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同样的,孔子所阐述的道德和理性占优势的学说在300多年内被大加改变,以至于到了汉代的时候,著名儒生董仲舒给皇帝宣讲了一种原理,在这个原理中,道德修养与一种阐释技术纠缠混合在一起,而这种技术所阐释的是在宇宙范围内出现的预兆和魔法实践。在每种这样的情形之下,后来形成的哲学总是会光耀几个世纪,在时间上也比较接近于我们的时代。然而,从理性上讲,后来的哲学却比它所要接续的早期哲学距离我们更加遥远。
关于孔子哲学,我们有两个基本来源。一方面是《论语》,此书非孔子所著,但其主要部分编撰于接近孔子的时代,并且是以他的弟子们所保持的传统为基础的。另一方面,我们有种种后来的著作(某些人错误地把它们的著作权归于孔子本人),这些著作从后期儒学的角度解释了孔子的思想。对于苏格拉底的思想传统来说,其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孔子哲学相比较。因为,一方面有柏拉图和色诺芬(Xenophon,他们认识苏格拉底)的著作,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有新苏格拉底主义对苏格拉底所缔造的哲学体系的详尽阐释。然而,很少有人会返回到新柏拉图主义那里,以期重建苏格拉底哲学。通常的做法是,人们更愿意去直接研究柏拉图和色诺芬提供的证据,以决定这些证据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可是,关于孔子,通常的做法刚好相反,绝大部分的努力是用在了如何使孔子的思想与后儒的形而上学相一致。为了扭转这种方向,并把我们的研究单独限制在早期资料上,我们必须先让自己做好相对来讲收获贫乏的思想准备。尽管我们的研究范围不甚广博,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解释在我们所限定的范围之内的材料的话,收获将会是真实的。
我们的第一个难题是关于孔子思想来源的问题。许多人经常认为孔子仅仅是力图复兴真实的或虚假的上古黄金时代的光荣。孔子弟子子贡宣称,孔子不需要普通意义上的老师,因为他能够知晓周朝前期统治者们(文王和武王)的学说。 [477] 孟子则说,孔子传递的是从神秘的早期帝王——尧和舜——传承下来的思想学说。 [478] 一位当代中国学者断言,孔子不仅是个保守派,而且事实上是个“反革命派”,因为(在这位学者看来)孔子的所有愿望就是取消发生在中国人生活中的种种变革,并复辟过去。 [479]
我们将在下一章对孔子独立于古人的程度作一个全面的探究。在此,我们则要预先说明,在我们考究了有关证据之后,将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孔子确实谈论古代文明,并从此资源中汲取了一些重要思想;但另一方面,他并未妄想要努力复古,并且他也未在古人的思想之中找到构成他的思想的那些最基本的概念。事实上,在一些重要方面,孔子是一位革命家,审慎的革命家。
我们已经看到,孔子出生在一个政治和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对于这一时代背景,尽管近些年来各个领域里的中国学者进行了卓越的研究工作,但从总体上讲,我们对此仍然知之甚少。在这个时代里,甚至艺术方面都发生着变革。如同孔子一样,艺术也在审视着过去的伟大日子,要从那里得到某种灵感。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指出:“西元前7世纪至西元前3世纪时期,中国社会已经进步得足以发生一场有意识的艺术上的文艺复兴运动,这场运动吸收了古已有之的和受人尊敬的因素……” [480] 艺术上的旧的东西被完全改变,以至于最终产生了全新性质的艺术作品,这与发生在思想领域里的事情如出一辙。
那么,在这场文化革命中,孔子的特殊作用是什么呢?确切地说,孔子并不是这场革命的发动者,因为这不是他所能控制的力量所导致的一场剧变,并且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之中了。某些学者认为,孔子在一定程度上碰巧因为某些观念而出名,而这些观念事实上是被他的时代之前的更有才能的人所创发的。在各种著作中,特别是在《左传》中所引述的几位生活在孔子之前不久的政治家的观点,正表达了酷似于孔子的思想。事实上,他们的语言有时与我们在《论语》中所看到的实质上是一样的。 [481] 很久以前,一些中国学者就指出了这个事实, [482] 其中的一个人还大力称赞这些政治家,认为他们的思想远比孔子更进步。此人不无羡慕地指出,在《左传》(好似真正的处世大百科)中,这些政治家在每个论题上都表现出了远见卓识。可是,此人却没有附加上这样的意见,这些政治家的知识太广博了,(根据《左传》)以至于他们能够以最令人不可思议的精确度预言即使是在未来一个世纪后发生的政治事件。 [483]
《左传》中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这种预见显然都是在事件发生后很久才写下的,而并不是那些预言家在当初讲出来的。许多纯粹的“儒者”之言(《左传》让它们从各种人物的口中道出)是在写《左传》时写下的,而《左传》问世时,孔子已去世良久,这些思想也已经变得很常见很流行了。
这并不是说《左传》之中的人物本身是不存在的。他们确实存在过,并且无疑也是有才能和有智慧的。他们可能有一些酷似孔子思想的观念,并且大大地影响了孔子的思想,这些都是相当有可能的。但我们并不能肯定这种相互关联是否在每个层面上都是完全真实的,因为我们没有在早期的和无可怀疑的著作中找到对他们的思想的说明。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孔子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他的某些近代前辈的思想的话,《论语》就应该有所揭示,甚至在他的对手的著述中也应该有所提及,但是,事实却是,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相反,传统说法强调了孔子思想的独特性。也就是说,在他自己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不断变革的社会中,孔子的作用是将那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革加以条理化和理性化,并以自己的意愿尽力抑制可能出现在这些变革中的那种他所不能赞同的东西。同时,孔子又力图指导中国文化走上他所相信的合理的道路。
为了探究孔子哲学的背景,让我们先来考虑一下他的宗教观。宗教通常是保守的,并且直到我们能讲到的时间上限为止,中国古代的宗教在几个世纪之内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西元前1122年以前,商朝的国王,可能还有别的人,都要劳心费神地祭祀他们的祖先和其他神灵,特别重要的是被称作“帝”的有权力的神灵。当时的人们相信,这些神灵,特别是他们的祖先,一同监管着世人的命运。他们在高兴时就赐予世人成功,不高兴时就以种种灾祸重责人类,这些灾难包括从战争的失败到牙疼。 [484] 商朝人的祭礼是为了避灾得福,并且他们不断地通过占卜查考他们的上帝们的愿望。
征服了商朝的周朝继承了商朝宗教的某些方面,并把商朝的宗教与他们的宗教相结合。周朝的主要神被称作“天”,这个汉字的早期形式是 (金文),明显是个高大的因而也就是个重要的人物。依靠种种证据,我们可以重建它的大概的历史。在周人看来,所有最重要的人物,包括去世的国王们,全都住进了上天。作为“上帝的顾问”,他们控制了人的命运。因为中国人不区分单数和复数,“天”就逐渐变成了单数,成为一个居住在天空中的占据统治地位的神。同样的一个“天”字,也用来指物质的天,天空。因此,就产生了一个相当非人格的理性化的“天”的概念。周朝征服商朝之后,把他们的“天”与“帝”(商朝的神)相合并,就如同罗马人把他们的神与希腊诸神相合并一样。 [485]
宗教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地位。国王被称作“天的儿子(天子)”,并依靠他们的德行进行统治,而这种德行的获得,据说是受了他的伟大祖先们的帮助。较低级的贵族之所以是贵族,就因为他们有强大的祖先。祭祀这些先人和其他有力量的神灵是国家的庆典。要想得到好收成,举行这样的祭祀比锄草更重要;同样,为了保证战争胜利,举行祭祀也比操练部队更重要。可是,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世故,怀疑主义的出现势在难免。改进了的交通使人们与各种各样的信仰和习俗相接触。那些被认为由神灵作过保证的协定不断地签订,又不断地被撕毁。但是,受灾受难的通常并不是毁约者,而是武备缺乏者。贵族世家陷入了失宠和贫穷,使人开始怀疑他们的祖先神灵的力量。我们对怀疑主义之所以出现的细节知之甚少,因为毕竟没有稍早于孔子时代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献,但是,这种思潮的出现是显然的。孔子去世时出生的墨子责备儒家的如下说法:“天是没有理智的,死人的灵魂是没有意识的。” [486]
孔子本人对宗教的态度是复杂的。对于他所赞成的传统宗教的某些方面,他会进行强调;但是,对于他所不赞成的另一些方面,他会努力予以改变或者加以抑制。总的来讲,孔子回避了已经出现的基本的宗教问题。这可以被解释为怯懦,或者被解释为睿智。事实上,孔子竭力去做的是进行他认为生死攸关的政治和社会本质的改革,这种改革的基础大半不是形而上学的。在形而上学问题上争论不休,既不合时宜也有碍于实现孔子的主要目的。孔子没有那样去做,而我们有时对他仅仅在言语上予以认定的东西也得存疑。
孔子显然对于盛行的种种宗教仪式表现出了几乎是孩子般的率直喜爱。 [487] 但这并不能表明他的信仰。其实,许多持有怀疑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喜欢“高教会派(High Church)”的仪式。孔子强调孩子有义务为他们的双亲守丧三年。 [488] 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一种过度的奉献。然而,这种观点并不能结论性地证明,这就是孔子对死后生命的信仰。事实上,孔子仅仅把这种行为看作是家庭团结的一个方面。
根据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孔子并没有正面讲过关于神灵的言论。事实上,有记载特别指出,“夫子不讲关于怪异现象(比如预兆)、强力的功绩、无序的政治和有关神灵的事情”。 [489] 孔子确实称赞了神秘的统治者大禹,因为大禹“向神灵表示了极端的孝敬”。 [490] 可是,当子路问他如何侍奉神灵的时候,孔子回答说:“你还不能侍奉人,又怎么能侍奉神灵呢?”子路接着问到了死,得到的答复是:“你还不理解生,又怎么能理解死呢?” [491] 弟子樊迟请教智慧,孔子告诉他说:“认真对待那些适合于人民的东西,还要尊敬神灵并与他们保持适当的距离。” [492]
上述孔子的最后一句话也被译作:“在尊敬精神存在的同时,要避开它们。”一些人认为,这正是孔子宣扬不可知论的清晰证据。但是,这种解释与多数中国注释家的理解是不一致的, [493] 这些注释家把它用作怀疑论的证据。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指出过,那些遵循相互尊重之原则的人们“彼此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我们不能说这种看法不应该适用于与神灵的关系。孔子的观点大抵是这样的,一个人应该适度地尊敬神灵,但不要过度奉承他们,正如对待国君或在上位者一样。 [494]
《论语》有几章讲到了祭祀,但它们并没有(只有一个例外,我们将在下文讨论)清楚地告诉我们孔子是否相信礼仪有实际功效,或者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有其价值。 [495] 可是,在孔子积极倡导的医治社会疾病的种种行动中,既不包含祭祀,也不包含其他宗教行为,这一点是意义重大的。孔子曾经自称是祷告者,但这说的是依靠行动而不是言语来进行祷告。所以,甚至在病重时孔子都拒绝别人为他向神灵祷告,并宣称自己(用行动)“做祷告已经很久了”。 [496]
如果我们去找寻孔子以确定而坦率的言语道出的部分地与宗教有关的信念,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孔子的“天”的观念。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是,在《论语》中,孔子没有提过“帝”这个字,这是个更具人格化的神的名称。 [497] 可是,孔子却把上天(“天”)看成是他的力量的来源。上天托付给他一项神圣的使命,要求他去做一个中国文化的卫士。在危难中,孔子击退了在面对上天时无力反对他的敌人。在消沉时,孔子至少以上天对他的理解来自我安慰。当因过失而受到责难时,孔子请求上天来证明他的无辜。在他的得意弟子颜回去世时,孔子宣称“天正在毁灭我(天丧予)”。 [498]
上一段的最后一句最好应被理解为仅仅是痛苦的呼喊,而并非意味着孔子以为上天针对他而采取了特别的和有恶意的行动。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他以这种方式表述过“天”,而在古代却有过这样的表述。在《书》、《诗》和早期金文中就有这样的文字,认为上天监管着王朝的更替,用消灭压迫性的国君家系来处罚罪恶,用更立良善之人作为被灭亡的国王的继承人来褒奖德行。这种著作认为,上天“等待五年”去察看一个罪恶的国王是否会浪子回头,并且还会“降下灭顶之灾”和变得“发怒”。周成王是周朝缔造者(周武王)的儿子,人们引述周成王临终时的话说:“天给我降下了疾病。” [499]
所有这些说法大抵又回到了“天”的原意,即“天”是伟大祖先们的合名,他们生活在上苍,无时不在监察后代的行为,并且随他们的意愿进行奖惩。可是,对孔子来说,“天”是没有人格的。孔子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所说的“天”到底是什么,弟子子贡说夫子不谈论“天道”。 [500] 然而,孔子显然是把“天”看成是一种非人格的道德力量,一种人的道德意识的宇宙副本,或者说是一种保证,即在一定程度上从真正的宇宙特性的角度肯定了人的正义感。
可是,这并不是说正义一定会取胜或者德行一定会成功。如果有人认为孔子真的相信他的事业有上天的保证,并且认为历史是由上天主宰的,那么,这一定是曲解了孔子的思想。我们从未发现孔子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德行一定会受到褒奖。他只是说,道德之行有助于得到好的结果,正如统治者的暴虐行为会促使他们垮台一样。显然,这种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联并不是简易的和必然的。确切来讲,德行的最大奖掖是它给德行之人带来的心灵的平静,以及由于帮助他人而获得的惬意。人之作为人而行动的理由不应该跟幸福与否直接挂上钩。“夫子说:‘一位君子,在制订他的计划时,想到的是大道;他并不是只想着如何过日子。即使去耕种土地,他有时也会挨饿;而如果他去学习,他就可能得到很高的俸禄。但君子关切的是大道的进步,他并不为财富而发愁。’” [501]
上述观点与我们通常在较早期的文献和青铜铭文(金文)中所看到的思想是非常不同的。在那里,宗教典礼和特殊的祭祀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几近乎一种物物交易。在《诗》中,因为王国被旱灾所蹂躏,一位国君就询问上天和祖先为什么这样折磨他。他说:“没有我不祭祀的神灵,没有我吝惜的牺牲。……为什么我的行为没有被承认呢?” [502] 我们反复研读《诗经》和《尚书》后得出的结论是,祭祀的目的就是要获得赐福。刻在上百件青铜祭器上的铭文相当率直地告诉我们,它们的目的就是祈福,如长寿长禄、多子多孙,等等。一座齐国的铸钟(大约铸于孔子出生时)上长篇地、详细地列举了铸造者希望从他的祖先那里得到的福祉,以求祖先回报他的孝敬。 [503] 生活年代稍后于孔子的墨子谴责了“供一头猪却要求一百个祝福”的行为。 [504] 但是,因为墨子确信神灵受到了祭祀活动的影响,所以很为这种不公平的交易所烦扰,这种交易就是,神灵根据他们所收到的供品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赐福。
孔子的思想与上述观念截然有别。在很早于孔子的文献中,确实偶尔有表述认为,德行和祭祀一样,都是用来取悦上天的。所以,如果要说孔子从这些著作中汲取了某些思想的话,他一定是只选择这一方面,因为他的思想着重点几乎过分讲求伦理了。
孔子也反对传统宗教的某些内容,比如,传统宗教非常看重的人殉(殉葬)。在商朝,大量的活人被献祭和殉葬。 [505] 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周朝。《诗》中至少提到两次,《左传》中有大约11次。 [506] 后来的著作中也提到了人殉。孔子在世期间,这种事情在有关记载中共发生过3次,其中的一次就在鲁国。稍晚于孔子的墨子宣称,那些倡导精心操办葬礼(厚葬)的人想要杀死一大批人(有个国王要多达几百人)去陪伴死去的要人。 [507] 当秦朝的“始皇帝”(秦始皇)在西元前210年下葬时,据说杀死了一大批后宫女子为他殉葬。 [508] 晚到西元前1世纪,汉朝的一个封王命令他的奴隶乐师为他殉葬,其中的16人在他死去时被迫自杀。 [509]
《论语》并没有提到人殉。孟子引述孔子的话去谴责那种甚至是以人像殉葬的做法,大抵是因为这种做法具有怂恿人们用真人殉葬的倾向。 [510] 《礼记》详述了一件事,即孔子弟子子禽在他兄弟的葬礼上制止了杀人。 [511] 儒者总的来讲反对人祭和殉葬,并最终取得了伟大成功。实际上,上述最后的一个人殉的例子就受到了舆论的猛烈抨击。尽管这位迫使奴隶殉葬的封王是汉帝之后,但他的儿子却未被允许继承他的封位,他的封地也被没收。指责他犯罪的言语显然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儒生不仅迫使人殉的做法走向没落,而且对于文献中记载的这种事情也予以消除。所以,当《左传》提到人殉时,总是要对这种行为进行谴责,并有几次说“在古代”并未实行过这种做法,意思是说它绝不是真实的。甚至到了20世纪,一些考古学家还拒绝相信商朝有过人殉,而直到在商代墓葬中发现了几百具被斩首的牺牲品骨架时才证实了殉葬确实存在过。可以说,儒者在这件事情上获得了如此的成功,以至于他们几乎销毁了自己所获成功的痕迹。
儒家在宗教方面的另一项重要革新几乎被忽略。在孔子之前,君主最重要的财产是他们的祖先。祖先不仅给了他们合法的统治地位,而且提供了诸神的帮助,使他们能在和平中成功,在战争中取胜。《诗》告诉我们说,周王室有“三位统治者在天上,而国王将是他们在首都的副本或变体”。 [512] 在一件青铜器铭文中,一个次一级的统治者把他的有名的祖先们吹嘘为“为他的后人气势磅礴地开辟了一条大路”。 [513]
孔子看不起所有这一切。在孔子看来,重要的不是世袭特权,而是一个人自身的品质。弟子冉雍的先人大概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程度的问题,可是,孔子却宣布,这并不会妨碍他从政, [514] 而且,孔子还认为冉雍是弟子当中唯一的一位适合于登上君主之位的人。 [515] 对于一个没有什么显赫祖先的人来说,这一观点是具有革命性的;它完全取消了祖先在早期宗教中所处的中心地位。
【按:这话说得不靠谱,先秦有名有姓的人祖上都是大贵族,不存在血统上的问题。正因为大家都有,才需要用德行和才能判断是否适合担任要职。祖先崇拜是一直都是中国信仰系统的核心组成成分~】
换句话说,一个人能否登上王侯之位,完全要靠他的德行和才能。这种观点明显是对道德行为的极大鼓励。当然,这种从宗教礼仪到道德思想的转变在许多宗教中都发生了。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一转变是很显著的。最容易使人想起的例子是希伯来先知之所为。 [516] 不过,使得孔子不同寻常的地方(如果不是唯一之处的话),就是他使道德脱离任何东西而独立的程度超出了所有知识分子的寻常理解。马克斯·韦伯说过:“儒学是如此范围广泛的理性主义,它在缺少所有形而上学和几乎所有宗教寄托的残余时,却能站立在人们有可能称之为‘宗教’伦理学的最边缘。与此同时,在缺乏和反对所有的非功利主义标准的意义上,与任何其他伦理体系相比,儒学更具理性主义、头脑更清醒;在这方面,可能只有杰·边泌(J. Bentham,1782—1832)是个例外。” [517]
【按:这里可以结合詹姆斯·斯蒂芬批驳边沁的功利主义的内容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应该指出,韦伯所讲的是儒学而不是孔子。不过,韦伯所说的缺少“几乎所有宗教寄托的残余”的论断亦适用于孔子本人。我们已经看到,在有关“天”的观念中,孔子确实保持了一种非人格性的道德之神的意识。孔子也有一种理想的宇宙和谐的意识。比如说,“有人请教禘祭的意义。夫子回答说:‘我不知道。知道它的意义的那个人,能够像我给你显示出的那样很容易地处理天下所有的事情。’——他指了指自己的手掌” [518] 。在这一章和一些别的章节里,很可能看到这样的证据,即孔子无意识地构建起了一种与宗教有一定关联的宇宙秩序。然而,孔子并不怎么强调这一点。但是,它是(用韦伯的词语)一种残余,一种古代全能神灵层面上的暗淡的副本。
与上述思想联系紧密的是“命”这个概念,英文译成“天命、天意(decree)”,通常译作“命运(fate)”。根据这种译法,“天命”即是“上天之命令”的缩写,尽管孔子很少使用后一种表示法。 [519] 《墨子》责怪儒家的以下说法,即:所有事情均受人的努力不能改变的命运的决定。 [520] 这种批评对一些后儒来说确实是真实的,但它不是孔子的学说。孔子把“命”这个词用作“生命”或“一生”的同义词。 [521] 但是,他明确认为这种“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和超越任何个人控制的,因为孔子讲过,一个人“在面对危难时,即使放弃生命”(字面上是“命”),也不能抛弃原则。 [522] 假使一个人的一生固定不变,以至于个人无所作为,那么,孔子讲的这句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论语》中有唯一的一章乍看上去似乎能使孔子成为一个宿命论者。那是在子路从政于季氏时,子路的一位朋友和同事告诉孔子说,子路的另一位同事向季孙毁谤子路。这位朋友提出利用他的影响要将毁谤者处死。但孔子告诉他说:“如果大道将要流行,那就是命该如此;如果大道要被抵制,也是命该如此。”孔子反问道,那个毁谤者又怎能奈何得了这个“命”呢? [523]
为什么孔子要以这种方式作答呢?让我们考虑几种可能的回答。孔子可以同意处死对手,但这与他的原则相反,因为他不相信建立政治派系和策划政治阴谋是一种良策。孔子也可以拒绝说:“你提出的方法没有价值。”但这会毫无必要地伤害和疏远一位好心好意的朋友。相反,孔子后退到引证那叫作“命”的普通概念,并且在没有伤害任何人之感情的前提下处理好了这种局面。
孔子自己既不依赖命运,也不劝告别人如斯行之。相反,他一再坚持个人努力的重要性,强调完成个人应尽的道德责任,以及为此而进行卓有成效的奋斗。 [524] 不过,《论语》仍有另外的一章无疑促成了儒学内部某些集群之内的宿命论的发展。这一章开头部分是:“子夏说:‘我听到有一种说法……’”这通常被认为是子夏引述了孔子本人的话。子夏接下去说:“死和生是因为命,富和贵依靠天。君子是庄重严肃的,并且从不抛弃他的责任。他有礼貌地与他人相处,并与礼保持一致。” [525] 引述这一章的人一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天”字上,但这样一来就会失去这一章的要点。生和死对一个人来讲是相对无能为力的事情,我们可以尽力延年益寿,但死亡真的到来时,我们毕竟只能服从,并且有时还会说:“这是命定的。”孔子就是这么做的,而我们今天也不会做得更好。为了得到富和贵,一个普通人是能去做点儿什么的,但一位君子却不能去做。作为一种努力追求的目标,荣华富贵是不配受君子注意的。“君子关切的是大道的进步;他并不担心贫穷。” [526] 尽管一个人对生死富贵之类的事情终究无能为力,但也不能草草地归结为完全是“依赖上天的”。一个人要做的是(这是子夏所说的后半段文字的重要性)注意他自己的品格和他的人际关系。
总之,这才是孔子对待宗教之态度的关键。从表面上看,孔子相信宗教的作用,但他对它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与超越了人的控制的强权王国打交道是出于无奈的。孔子真正感兴趣的是把一个让人不能忍受的现实生存环境改造成一个良好的世界,他不去做那些与他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他忙于真正的实际问题,那就是:如何尽力利用我们所具有的实际能力,有效地做出具有实际收获的行动。
孔子哲学的中心概念是“道”。我们经常提到这个概念,但却一直没有正面描述过它。在大多数的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道”逐渐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但在孔子那里却并不是这样。
汉字“道”一般译为“道路(Way)”,但在商朝的甲骨文中还没有出现此字。 [527] 在较早于孔子时代的金文中,也很少使用这个字,而在使用它的地方也只有两种意义:原意“道路”,以及用于一个专有名称。 [528] 在前儒家的所有文献中,这个字总共只使用了大约44次,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在《论语》中出现次数的一半。在这种较早的文献中,它多半是“道路”的意思,很少与(从“向导”中产生的)“行为”和“说道”的意义相联系。它有6次是“行动路线”的意思。 [529]
《论语》中的“道”以上述所有的意义出现,但却几乎总是偏于“行为之道”的意思;其他的意义是稀少的。在《论语》中,“道”用在坏的方面,也用在好的方面。孔子还讲到过不适宜的道。 [530] 至此,我们并没有得到新东西。但是,其中有一个在前儒家作品中没有的先例,就是用“道”意指高于所有其他道的“那种道”,作为区别,我们也许可称之为“大道”。只是孔子心目中的这种意义才使他说出:“一位大臣要根据大道事奉他的君主。” [531] 正是这个具有新意的汉字“道”,才是《论语》中最常用的。
孔子认为,这个大道是个人、国家和世界的行动道路。如果“全天下(即当时的中国社会)都有了大道”,或者某个特定的国家“有了大道(有道)”,这就意味着它们被治理得就像它们应该是的那种状况,并且道德原则大为流行。如果某个个人“有了大道”,他就会像他应该做的那样去行事,并且是个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可是,这个概念并不像这番描述所讲的那样枯燥无味。
孔子有一次说:“我的道是由一项单独的原则贯穿(“贯”,字面意义是“用线串”)起来的。” [532] 这是一项什么原则,我们从未被告知。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论语》,那么,在大道的历史背景中,我们可以足够清楚地看到它。它是一种对协作社会或大同世界(cooperative world)的洞识。它的信条是,敌对和猜疑、战争和灾难,都是极其不必要的。它是一种深沉的信仰,即:人们的真正利益不是相互冲突而是互为补充的,所以,诸如战争、不公正和剥削之类的行为,既伤害那些从中受益的人,更伤害那些直接受其磨难的人。实际上,这是“贯穿”整个孔子思想的一条线索。以此线索,可以用逻辑演绎推导出孔子的大部分哲学。根据大道的洞识,一个较好的社会终将变成现实,所以,“道”的概念并不是教导人们不犯错误的枯燥无味的规则,而是一个原则实体,它要求人们采取积极的并且有时是冒险的行动。
在最近的研究中,洛兰·克里尔(Lorraine Creel [533] )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道”的思想的深远意义,其文如下:
“道”是孔子认定的个人和国家的理想生活方式。它是一种生活之道(方式),包括了所有的德行、真诚、正义、慈爱和喜好。它全神贯注于礼和乐的原则。可是,像人的身体一样,它并不是各部分相加的总和,因为它依靠一种“突创的合成”获得了它自己的品质和力量……
尽管法律提供的行动标准比一个有德行的君主更稳定、更持久,但“道”所提供的行动标准却比法律还要稳定和持久。法律依赖政治实体的种种异想天开并从该实体吸取其权威。但另一方面,“道”却完全不依赖任何政府,它从自身汲取其权威。所以,在像春秋(前722—前481年)和战国(前468—前221年)这样的无序而混乱的时期,它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它提供了共通的行为标准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在它之上并没有中心权威。齐国的君子和鲁国的君子都可以把“道”看作他们的行为准则。
“道”也高于法律,而法律要求的仅仅是行为的最低标准……“道”不仅禁止人们杀害或伤害邻人,也要求人们以友善和互相帮助的态度对待他人。这可能与“道”不使用强制手段发挥其作用的特点有关。如果因为不能与标准取齐就乞灵于惩罚的话,法律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标准,以至于人民群众不能与之取齐……“道”不使用强制手段的另一个事实是,它并不是依据自我的利益来激发人们的德行。因为它不是用奖赏或惩罚去鼓励个人为善,就不会使个人转而注重自身并看重自身的利与害。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一旦个人设定说,他自己的利益是行动的终极目的,那么,只要好处胜过劣处,他就会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乎道义的。
如果个人的追求就是遵从“道”,自我及其利益便不再是注意力的焦点。他的行动准则变得与“道”而不是与自我利益相一致。与此同时,他的行动不再是孤立的,并且只有参与众人的行动中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大家现在通过对“道”的共同聚焦而联系了起来。同样,因为他把自己看成是人群中的一员,也就能把自我置于一种历史发展之中;处在人群之中的人们可能有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但他们都对“道”的进步感兴趣。 [534]
当孔子讲到“有”大道的人和国家时,这看起来像是说他把大道构想成了一件东西,可能是个形而上学的实体。这种观念很适合于去做这样一种构想,而后来的中国思想界也确实这样去做了。可是,孔子认为,“道”所要保持的是一种行动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行动的大道。其证据正如他之所说:“如果没有门,谁能走出屋子呢?为什么就没有人来遵从大道呢?” [535] 孔子显然认为大道具有最高的重要性,在那著名的一章里,“夫子说:‘如果一个人在早晨听到了大道,他就可以毫无遗憾地在晚上死去了。’” [536]
因为大道概括了孔子的哲学总体,孔子便从未清楚地定义过它。而我们要想理解它,就必须把孔子哲学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为此,我们可以去了解作为它的中心思想之根源的某些东西,也就是关于协作社会的观念。孔子哲学的根本基础很可能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在人类世界的诸多文化中,“家(家庭、家族)”都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很怀疑会有什么地方,会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比中国的思想界更看重家的问题。其重要性的某些方面,特别是裙带风、门阀主义的泛滥确实是很让人叹惜的。然而,从尽力使中国文化令人瞩目地保存下来这方面来看,家这一社会单元可能比任何其他社会机制做得更多。在许多社会问题的初期阶段,家就处理了它们。正因为有了家的功效,中国才形成一个由数量巨大的几近自治的社会细胞所组成的稳固的社会,这些细胞所发挥的作用甚至很少受到民族大变动或江山易姓的影响。家已成为道德的保育箱和国家的缩影。从某种角度上看,儒学可以被定义为中国家族制度的哲学。
就家的哲学而言,孔子并没有添加新东西。 [537] 从甲骨文给我们(并不很多)的显示来看,家甚至在商朝就是很重要的。周朝文献也不断强调家的基本重要性。可是,在早期文献中,我们对于普通人的家庭状况确实是知之甚寡。因为在当时社会中,贵族家庭是主导性的,而他们的地位则要仰赖其祖先。在战争中获胜的周王,他的统治地位被封建制和家族联系的网络所加强,而这些联系则通过近族联姻和对忠诚的亲戚的分封而不可厘清地融合在了一起。周初的统治者们完全意识到了家族在维护其统治秩序中的根本作用。《尚书》有一部分是周公(孔子把他看作是大道的早期先驱)对他兄弟的谕示。周公教训他的兄弟要用大道治理他即将统治的领土,并严令他特别注意管理好自己的家族。周公强调说,如果臣民不尊重家族联系,“上天颁给人民的(道德)原则将会陷入无序之中”。周公还宣称,不孝和不悌比盗贼和谋杀都严重,必须受到毫不宽大的惩罚。但最重要的是,不仅不孝之子而且是不慈之父,不仅是横蛮之弟而且是专横之兄,都应该受到谴责,都应当受到惩罚。 [538]
早期文献不断强调“孝”的义务。当死去的先人控制了人的命运时,孝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孔子把孝解释为一种社会义务,但还是对其予以高度重视。当然,在服从父兄和遵从大道之间是有潜在冲突的。要是这两者之间不一致时怎么办?孔子对此言之甚少。他只是有一次说,一个人可以“劝谏他的父母,但要温和有礼”。 [539]
在另一章中,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冲突。“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里有这样一个正直的人。如果他父亲偷了羊,儿子就会指证他。’孔子回答说:‘我们那里有相当不同的正直行为。儿子庇护父亲,父亲庇护儿子;我们把这看成是正直的品行。’” [540] 这种冲突确实存在,甚至在西方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你得知你的父亲犯了杀人罪,你要告发他吗?孔子并非不清楚社会的要求,但他把家庭放在了首位。可是,后世书籍中的一项记载是令人怀疑的,这项记载认为,孔子曾告诫某人向杀害他亲戚的凶手报“血仇”。 [541] 孔子不相信家庭和国家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因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孔子认为,正是在家庭之中,个人才学会了服从和协作,并得到了让个人的行为社会化的经验;也就是说,在家庭磨炼的基础上,个人才有可能去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公民或官员。 [542]
在中国,孔子并不是看到家庭、家族与国家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和接续性的第一个人,有两首较早的“诗”把君主看作是“民之父母” [543] 。这种表述在许多地方是十分普通的,但重要的问题是,它们意味着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持久不衰的家长制几近乎专制主义的同义语。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种观念曾经对早期的很多普通中国人起过多么了不起的镇静作用。可是,在儒家运用这种观念时,它却变成了社会改革的强大力量。
在家和国家相类似这一点上,孔子无疑被以下事实所吸引,那就是:家是一种有秩序地服从权威的模式。但是,另一个方面很可能对孔子更有吸引力。中国的家是个组织,在其中,每个成员生来就跟别的成员“一样好”。这不是说家中就没有从属关系。孩子们当然要服从家长的权威,但是,总有一天,孩子也会成为家长。在正常情形下,长子以下的儿子们不会成为家里或家族的首领,但这一事实并不表示他们有什么毛病或污点。任何年轻人都可以在家庭事务中表达声音。经济利益也会相当平等地分享。如果某一位家庭成员受到不公正待遇,他会提出抗议,并有相当的成功机会。从理论上讲,家长相当于专制君主。但在实际生活中,家长很难固执己见地跟那些与他朝夕相处的大多数家庭成员作对。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家庭在理论上是君主专制式的,而在实际中大体上却是民主式的。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其成员就是“我们这群人”中的成员,他们被视为目的而非手段。他们之间是有从属关系,但每个人都有他的位置、他的作用和他的尊严。
孔子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进入这样的状态、这样的社会。这其实也就是子夏所述的意义之所在。子夏曾听说(几乎可以确定是得之于孔子):“在四海之内,所有的人都是兄弟。” [544] 事实上,对于那些在文化上与中原之人有所不同的“蛮夷之人”,孔子并未表露出任何程度的沙文主义倾向。韦利甚至认为,正是孔子才把这些人“一定程度上理想化为‘高尚的野蛮人’”。 [545] 孔子确实乐意他们以中原华夏文化为标准而变得“文明化”,因为孔子的理想国的范围是整个世界。很有意思的是,当国际联盟正在筹备的时候,应威尔逊总统的请求,康有为阐述了他对孔子关于世界国家(大同世界)的观点的理解。 [546]
孔子坚持认为,就在他的时代,所有阶层的人们都应该拥有他们自己的价值,他们绝对不能被仅仅视为国家实现其目的的手段,而应该被看作是国家存在的目的,这显然是一种更具革命性的思想。孔子对此一点的坚持可以从以下事实清楚地看出。他说,政府的目的是造福于民。 [547] 弟子有若有这样的思想,即:国家是共同的事业,它所有的好运或恶运、高潮和低谷,都应该由大家分担和分享。鲁哀公说,因为年景不好,他不知道如何提高税收,以保证自己有足够的开支,请有若给出个主意。有若建议他征收十分之一的税。鲁哀公回答说:“(原来的)十分之二我还不够,现在怎么可能只收十分之一呢?”这位孔子弟子的答复是:“人民富足时,你怎么会受穷呢?但是,你的人民受穷时,他们的君主又怎能安享富足呢?” [548]
与那种由强制手段所支配的社会恰恰相反,在一个由(有限度的)自由行动者组成的协作社会中,个人是至高无上的。社会不过是组成它的个人的总和,然而,如果其中的重要部分是缺乏道德的,这个社会就是很危险的。这样,孔子就以个人为开端,强调了自省、道德修养和教育的必要性。 [549] 孔子专心致志于对那些他希望他们去从政的人们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而万事开头难,最重要的是事情的起始处。但是,仅仅指出这些是不够的。《论语》中有好几章明确指出,孔子的目标包括了对全体人民的至少是某种程度的教育。 [550] 从孔子思想来看,这是逻辑的必然。完全无知之人可以盲目从命,但他们不能合作,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合作。因此,孔子说:“让普通人去学习大道,他们就容易被指挥。” [551] 通过受教育,人们易于被促使去做对大家都有益处的事情,因为他们对于发布给他们的命令,对于他们的行动目的和如何实现这些目的,都有一定程度的主动理解。 [552] 近来关于军事训练的讨论强调了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其理论基础就是,知道为什么而战的士兵将会更好地去战斗。孔子以如下方法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让没有受过教导的人民去作战,就等于是抛弃了他们。” [553]
孔子教育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修养品格,换句话说,这种教育就是要使求学者养成这样的德行:忠诚、诚实、守信、公正、仁慈、与礼保持一致,以及其他等。 [554] 当然,孔子所要求的忠诚,并不是单纯地忠实于某个个人。孔子特别谴责了种种封建式的盲目的个人效忠。 [555] 在孔子的理想中,合格的大臣应该是这样的人,他们与大道保持一致,尽其所能地尽量长时间地侍奉君主;但是,当不得不在大道与官位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应该坚守大道而辞掉官职。 [556]
这种对原则而不是对个人的忠诚是民主制度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那么,随便一个可以聚集起追随者的将军或政治家都可以不断地任意摆布一个国家。儒家提出了这样的忠诚原则,就意味着树立起了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之一。正是这种对原则的忠诚,才使后来的台谏制度或都察院之类机构的出现成为可能。在过去两千多年当中,中国政府中的这个机构承担了批评玩忽职守的官员甚至皇帝本人的作用。由于有了这项忠诚原则的支持,该机构中的某些成员(御史)才会无畏尽责,甚至在明知奖赏他们的英勇行为的将是流放或死亡的时候,他们也会毫无惧色。尽管诸如此类的传奇故事夸大了御史们反对皇帝的频率和作用,但是,这种传说的存在本身却是意味深长的。 [557]
对于那些为了忠于原则和恪尽职守而抛弃其他一切的人们,孔子答应给他们的奖赏是什么呢?是富贵和权力吗?都不是。孔子认为,荣华富贵不仅是不牢靠的,而且,对于君子来说,从他所控制的对象那里捞取好处是有损于尊严的。 [558] 是死后不朽的名声吗?孔子从未提到过。那么,在这个世界上,那些“见到危难,就献出他们的生命”(见危授命)的人,他们的所求、所愿是什么呢? [559]
在孔子看来,人的追求应该是:修养道德和实践德行,以及热爱大道并倾其全力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它。只有这样去做了,才可以说是完成了人的全部义务。贫穷不能奈何怀有这种追求的人。孔子说过:“吃粗糙的饭,喝着白水,曲臂而枕,我在此中仍然很快活。” [560] 如果一个实践大道的人不能得到高官,那么,造成这种不幸的可能是他在其他方面做得还不够好;但是,如果他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得很好,那么,原因就不在于有德行的个人,而只在于不任用他的政府了。“夫子说:‘不要在意你不在位,而只要求你自己能称其职;不要在意你未被赏识,只去寻求你自己的当之无愧。’” [561] 正是在此意义上,关于孔子的一种说法才是真实的,这种说法认为,孔子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明知道自己尽力去做的是不可能成功的事,却还在继续努力。” [562] 对成功机会的精打细算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引述孔子的话说:“如果审视我的内心时我是正确的话,即使有千百万人阻挡着我,我也将勇往直前。” [563] 这就必然得出结论:如果一个人决定了他应该去做的事情,他就要倾尽全力去完成。
因此,孔子提供了最无价的财富:心灵的平静。“如果一个人在内省时并未发现有自责的理由,他为什么要忧虑呢?有什么要惧怕呢?” [564] 孔子把心灵的平静放在了每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使它与外部世界的变幻莫测毫不相干。孔子问道:“德行是遥远的东西吗?如果我真的想要德行,它就会在眼前。” [565] 个人拥有一种庄严的意志自由,他的内心就是他的城堡。“即使是一支大军的统帅也可能被绑去,但没有力量能夺去即使是一个最卑贱之人的意志”。 [566]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它使得儒生“在国家有道时就去从政,国家无道时就收拾起他们的原则并把它们保存在胸中”。 [567] 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它也使得儒学能够与产生它的时代暂时告别,不为公众所知,而只是作为一种学者个人的学问继续存在着,并且一直把这种局面维持到汉代。
个人的自我满足,在理性的范围之内是善的。但如果它走得太远,就会隔绝一个人与他的同胞的所有联系。那么,一个人如果放松了他的原则,变成大众中的一员,就会成为“好人”了吗?不!孔子说:“不要在那些比你(道德水平)低的人们中间选择朋友。” [568] 这就提出了一个常见的难题,即:道德品质上的成就是依靠把每个人都降低到普通水准上来取得,还是靠提高大众的水准去获得。孔子坚定地支持后者的路线。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孔子将自己完全与众人隔离;事实上,在他的人际交往中,与他的某些受人欢迎的弟子相比,孔子更为自如一些。在这方面,孔子的主张与康德的自述很相似。康德写道:“人的义务就是……为自我建构一个坚定的原则的中心,还要以这个自我为中心画个圆圈,而此圆圈亦是一个囊括一切的世界性共鸣圈中的一部分。” [569] 孔子认为,人应该“善待每一个人,但只与有德行之人相亲近”。 [570]
然而,仅仅怀有善意是不够的。要是我们真有德行,就必须为他人做些什么。弟子曾参有一次陈述道,老师的学说除了“诚实和互惠(忠、恕)” [571] 之外再无别物。理雅格很自由地(但却是对其真意的敏锐感觉)把这一句译为“要忠实于我们本性中的诸种原则并将它们仁慈地施之于他人”。孔子所说的“恕”是一种应该时刻实践的原则,他自己把它解释为“不想让别人对自己做的事,就不要做给别人”。 [572] 这一原则有时被批评为仅仅是一种消极的观念。无论这个原则是非如何,孔子的确没有把人的义务构想为仅仅是消极的。他说:“真正的德行之人,要想成就自己,就得寻求成就他人;要想使自己成功,就得努力帮助他人成功。真正地实现德行的方法是,要寻求一个自己内心的愿望,并以此作为对待他人的行动准则。” [573]
读者马上就会想起康德所阐述的著名的绝对命令:“假如依照你的意志去行动,你的行动准则将会成为普遍的自然律。” [574] 虽然这个断言在表达形式上更精到一些,但却与孔子的原则具有相同的原理。从个人的角度看去,作为个人主义者的康德和孔子都把世界看成是由自我和外界这两大部分组成。一个人的自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他的责任,对自己来说终究都是无限的。所以,他必须以坚持不懈的努力陶冶他的品格。在自己这样做的同时(并获得了什么是善的知识),他必须竭尽全力地帮助所有其他人实现这个善。因此,康德断言,我们的道德义务要争取两个目的:“我们自己的完善、他人的幸福。” [575] 这一断言完全可以用来概括《论语》中的道德训诫。
这是一种严格的和理性的学说,但却对人性表现出了引人注目的乐观主义。如果一个人有义务“恕”以待人,就会得到人们的回报。实际上,这是协作社会的必要条件。孔子的确相信人们具有这种回报的能力。他认为,真君子的典范影响是那样地有力,以至于即使是身处野蛮人之中时,他们也不会受到粗暴无礼的待遇,因为那些不文明的表现都由于他们的出现而消失了。 [576] 孔子告诉鲁国的季孙不要使用死刑,理由是:如果他的愿望就是人民的愿望,人民自然会从善如流。 [577]
可是,我们不必太死板地看待这些微妙的句子。后一个表述的重点是讲求社会秩序,因为它是讲给一个专制统治者的,此人刚刚提议用杀戮的政策去除所有那些“错误”思想。但孔子知道,社会完善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事实上,在其他地方,我们发现孔子同意以下观点:如果让善人去治理一国,也得用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能除去死刑。 [578] 同样,我们也不能太看重以下表述:“夫子说:‘一个具有真正的生命价值的人是正直的;如果失去了正直,他只是侥幸偷生罢了。’” [579] 其实,孔子也深知,如果他所说的这项原则是不可动摇的,那么,在他的时代,世上便满是侥幸之人了。
孔子显然认为,人具有某种向善的趋势和受教育之影响的巨大能力。他说:“只有最聪明的和最愚蠢的人才不能被改变。” [580] 他也认为,有些人是那样地恶劣,以至于不值得为他们而浪费时间。 [581] 尽管孔子说过:“人的本性非常相似,但在实际活动中就逐渐变得非常不同了。” [582] 但他似乎并没有解决人是否天生就是善或者是恶的问题。可是,有些人却认定,孔子相信某些人“生来聪明”,一出生就禀赋有知识。事实上这是极其不可能的。 [583]
那么,人们是怎样获得知识的呢?更为重要的是,当人们获得知识之后,又怎样对知识做出评价?如何去伪存真呢?还有,什么才是德行呢?据说人们应该实践大道,但人们又是如何识别出什么是大道呢?衡量所有事物的最高标准是什么呢?这些可能是可以向任何哲学发问的最具探索性的问题。而当我们请教孔子时,我们大大地吃了一惊。
孔子并没有这类标准。
孔子并没有说一个人只需要遵从古人,诸如神秘的尧、舜二帝就够了。孟子这样说过, [584] 并且被认为是由孔子首肯了的。但是,在《论语》中,孔子并没有诸如此类的表述。孔子并没有说真理的标准就在某一部书或某一类书中。孔子自己并不把书籍依赖为他的思想的单独源泉,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劝告别人去如斯行事。尽管儒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开始对某些书籍(经典)表现出绝对的尊崇,但有证据表明,这一倾向也只是后来才出现的,是现实的思想发展中从孔子本人的学说之基础往后倒退的一部分。 [585] 最后一点,孔子并没有要求人们把他自己的话语当成终极权威。相反,他没有自称一贯正确,而是允许他的弟子们与他的意见相左,并认为这种不同的看法是无可指责的。
孔子从未在《论语》中说过,古人或某些书籍提供了真理的终极基础。不过,仅凭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他没有这样想过。确切讲来,这方面的有关证明来自以下事实:甚至在辩论中处境窘迫时,孔子也从来没有向任何古人或任何书籍发出过求助的呼吁。 [586]
在《论语》中,孔子一再声明他没有这样的真理标准。“夫子完全摆脱了以下四种做法:他不下定论,不过分独断,不顽固,以及从未仅仅从他自己的角度出发看待事情。” [587] 孔子自称他痛恨冥顽不化。 [588] 他有颇具柔韧性的名声,他的行动总是依据着对有关情状所作的仔细考虑。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的伟大,以至于孟子在一百年后详细讨论了它们,并称孔子是“适时的圣人(圣之时者)”。 [589] 孔子自己对此一原则的最佳表述是:“人世间真正的君子,既不预先倾向于任何东西,也不预先反对任何东西。他将站在符合道义的任何东西一边。” [590]
说到这里,我们遇到了孔子思想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义”。这个概念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正义”或“公正”之类的普通意义。 [591] 它的意义毋宁是适当和合适。当弟子有若说“如果一个人所做的诺言接近于义,他的话语才可以被履践”时, [592] 他的意思是,一个人在同意做某件事情之前,他应该考虑所有的情形,并且只能做出合适的和恰当的允诺。正是在与此相似的意义之下,孔子才赞成人的这种行为,即:当他“看到一个有所获得的机会时,要想到义”。 [593] 如果一个人为了得到可能的利益,根本不顾及他会因此而破坏信义、伤害到其他人,或者一意孤行地在某种情况下以某种不适当的方式行事,他终究会蒙受耻辱的。
这个“义”的概念所体现的显然是极其重要的道德力量。与“礼”和“道”相似,“义”也是一种行为标准,并且不断地把一个人自身的责任直接放在这个人的面前。大道是总体性的。一个人也可能指望在有关大道的问题上得到别人的某种指导,但是,在每种具体的情形下,怎么做才是适宜的呢?这却是每个人必须自己做出决断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例子,即孔子接受了这种适宜性的准则的指导。 [594]
然而,问题仍然追迫着我们:人们怎样决定什么是适宜的呢?依靠沉思默想吗?“夫子说:‘我曾经一整天不吃饭,一整夜不睡觉,以便于沉思。但那没有什么用处。最好还是去学习。’” [595] 但是,单纯的学习也不是答案。“夫子说:‘学习而不思索是徒劳的,思索而不学习是危险的。’” [596]
《论语》中的几项陈述描绘出了孔子认定的可以获得真理的方法。“夫子说:‘我不是那种生来就有知识的人。确切来讲,我喜欢过去,并勤奋地求取知识。’” [597] 探求过去仍旧是我们主要的知识源泉之一,但这必须是讲究方式方法地去做。“夫子说:‘我能讲一些关于夏朝之礼的事情,但杞国(一个据说是被夏朝国王的后裔统治着的小国)没有关于它的适当证据。我能讲一些关于商朝之礼的事情,但宋国(商朝后裔的封国)同样缺乏这种证据。……如果证据充足的话,我就能用可靠的证据对它们进行描述。’” [598]
可是,并不是每样东西都是同等可信的证据。对于一个想知道在实际政治中如何行事的学生来讲,孔子说:“多多地去听,但要把有疑问的搁在一边,并要小心谨慎地讲说其余的,依此而行则很少招致责难。多多地去看,但要把弄不清楚的搁在一边,并且仔细地履行其余的,这样就不会有后悔的时候。” [599] 我们一定要总是睁大眼睛,从经验中学习能学到的一切。然而,我们不能期望理解每样东西。我们必须理解我们能理解的,而对余下的则保持着有保留的判断。因此,孔子称赞那样的古书誊写者,当原文字迹不清时不是去猜测,而是“在文本中留下空档”。 [600] 孔子用如下言语描述他自己的求知之道:“去听大量的东西,选择其中的好的,并遵从它;去看大量的东西,并记住它们。这些是获得知识(或智慧)的几个阶段。” [601]
到此为止,孔子听上去很像是那种所谓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完全依赖经验获得知识。可是,孔子也曾问弟子子贡说:“你认为我的求知之道仅仅是学习许多东西并记住它们吗?”“是的,”子贡回答,“难道不是吗?”孔子的答复是:“不是。我有一条原理,它像是一条绳子,我用它把所有的东西都贯穿起来。” [602] 在此,孔子听起来又像是个理性主义者,根据自己内心的原则,设法整理现实世界的种种事物和现象。事实上,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孔子部分地是经验主义者,部分地是理性主义者。
【按:在我看来,遵从经验办事才是理性的表现,出问题的话纯粹是因为条件不同了。认为自己足够理性就能让处女生孩子就像认为自己是万能的却造不出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一样充满喜感~】
然而,这些仍然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什么是真理的标准?而我们从孔子那里根本得不到这一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们去当面征求孔子的意见,他无疑会回答说,每个人一定得自己去寻找这样的答案。在一个真正的协作社会中,这是唯一可能的答案。一架机器可以被操作,但却不能进行协作。在一个有着固定的真理和权威标准的社会里,个人的作用不会比一架机器更有创发性。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不论是拒绝整齐划一,还是接受整齐划一,他都不可能做出真正的贡献。如果人们对社会的成就负有责任,他们一定得要有机会去帮助社会选择其目的,也就是发现(不仅仅是揭示)真理。因此,康德清楚地看到,任何人要想达到完全的个性发展,“他就得有权利根据他自己的义务观决定自己的目的”。 [603]
说到这里,我们又返回到了个人。那么,我们能做出决定说,任何人都具有和其他人一样的判断正义与真理的能力吗?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我们在此正在面对的是一种思想类型,一种与科学相类似的思想类型。像孔子一样,科学家之所以看重经验,是因为他们在经验中获得的资料和进行的试验都与某种普遍性的假说或假说系列有关联。科学家也相信,一个正常人基本上具有与别人一样好的潜在的真理判断力。在科学家看来,高贵的出身和拥有一千万美元不会增加一个人的尊严。会增加其尊严的唯一的东西是受教育、拥有经验和被证明了的能力。
孔子做出了相似的判断。他相信所有的人潜在地来讲都是平等的。他既不畏惧权贵,又不藐视贫贱。而持有这种观点的人都认为,要想让人尊重,他们就得靠学习知识和修养道德来实现他们的潜能。这就是说,一个有知识的人的见解要比大批没有思想的民众的看法更重要。 [604]
为了防止误解,必须清楚声明,我们在此并无以下意图,即认为孔子“预测到了现代科学的方法”。在某些方面,孔子的思想相当缺乏科学观念, [605] 这并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但是,孔子的某些思想特征,比如说,对教条和定论的反对,对保留性判断的必要性所具有的清醒认识,以及对理性民主的拥护,等等,都说明他率直地接受了科学思想的最低哲学条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样一来,人们可能会问,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在很早以前就发展出科学方法呢?这可能或不可能是实情,但正如我们所述,孔子思想的这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很快就从儒学中消失了。
就像孔子思想一样,科学并没有不变的真理标准。科学是在寻求真理,并不是从一个预定的公式中推断真理。然而,这并不是说科学对我们寻求真理一无帮助。它并未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而是给了我们大量的如何寻求真理的忠告。孔子亦复如是。
确实没有多少哲学家,或者是没有多少比例的前科学时代的哲学家,能像孔子那样地如此强调灵活性。在西方,我们倾向于认为真理是一成不变的,并认为一位神灵或一位真正的智者一定拥有绝对真理。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人(通过希伯莱人,他们成为西方世界的理性祖先中的一员)认为不变性是敬神的标志,“如同神的言辞一样,国王的话是正确的,是不能改变的”。 [606] 我们通常认为,一个人改变他的想法和承认自己的错误会有损于他的尊严。如果有人真的这样做了,就说明他还没有拥有不变的真理。
然而,孔子却有不同的主张:“犯了错误,还不去改正它,这才是真正的过错。”“如果你犯了错误,不要害怕承认这个事实,而是要改过自新。”他反复地强调这个主题。弟子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可以比作日蚀和月蚀。当他犯错之时,人人都能看得见;当他改正之时,人人都仰望他。” [607]
当然,在一个允许有保留性判断的国家里,这种随时改变的准备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个必要方面。可是,同样是在这种国度里,做一个贵族可能就不很舒坦了。比如说,某个人每天都在一所住宅前的人行道上行走,并希望这条路不要有什么变故。然而,有一天早晨,如果这条人行道上明显出现了一个裂开的洞,这个人将会(让我们希望!)对新的情形做出回应并远离险境。可是,事实上,在某种情势下,人行道的下面可能会被掏成空洞,尽管这条路看上去仍很结实,但实际上却成了个陷阱,只是等着某个人上去把它踩塌。虑及这种可能性时,这个人需要改走大街——而大街上的危险可能会更大吗?当然,如果他对此过分惧怕,他甚至会因噎废食的。没有人(除了一些精神错乱者)会做出任何诸如此类之事。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评估在任何特定情势下的成功或失败、安全或危险的可能性,并以此判断而行事。我们随时这样去做,这是我们的生活之道。这些判断是个人的,所根据的都是我们先前的训练和经验,而且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人们可以搬出他所知道的全部理论,但归根到底,在某个时候他不得不在两种或更多的可能路线中做出选择,并希望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同样地,我们必须画出一条关于有保留地做出判断的实际界线。例如,假定有这样一种说法:因为我没有把握对某种情势做出绝对确定性的判断,因此,当我的邻居挨饿时,我就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有义务馈食给他们。显然,这种说法就是不对的。孔子认识到,需要为知识(“知”)画出一条实际的界线。他把“知”定义为:“当你知道一件事时,要承认你知道它;而当你不知道时,就承认你不知道它。” [608] 从上述所论很清楚地看出,孔子没有在绝对的意义上使用“知”这个词。确切来讲,他坚持了一种必要性,即在难以保证的怀疑主义和无所不包的教条主义确定性之间求得一种理性和适中的平衡。
对于孔子来讲,这种保持适中道路(持中庸)的求得平衡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孟子告诉我们:“孔子不走极端。” [609] 我们在《论语》中读到:“夫子说:‘我知道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不循中道而行,也不以中道实践我的原则,所以,我就把他们看成是激进者和过分拘谨者。’” [610] 孔子认为,这两种人具有同样糟糕的短处,“走得太远和有所不足一样有害”。 [611] “夫子说:‘中道实际上是最高的德行之道;但长久以来却很少有人去实践它了。’” [612]
孔子在此论述的基本上是一种讲求折中调节的哲学。在西方思想中,有一种不喜欢折中调节的倾向。这源于以下观念,即:真理和德行在一定程度上是恒定的和绝对的东西,智者和善人已经为此而建立了共识,并且他们将会一丝不苟地依此而行。孔子也认为,一个人必须画出一条界线,他不会因为折中调节他的原则而超越此界线,即使会以死亡作代价。但是,虽然孔子从未亲口讲述过真理是否会有变化,他还是相当清楚地肯定,只要我们还在继续不断地进行思索和道德修养,我们对真理的理解一定总是在变化之中的。而且,没有一个人有权利把自己看成是独一无二的真理的天定卫士。如果你的观点不同于我的,我们必须对此进行讨论。可能我们双方的观点中都有一些真理,或者是有某种近乎真理的东西可能就在双方的观点之间。当然,这种折中调节在逻辑上必然遵从以下概念:世界是协作性的,而这种协作性是民主政治所必需的。
【按:中庸不能和折中等同~】
进而言之,即使我的确掌握了某一方面的真理,这也不会自动告诉我如何在有关的具体情势中恰当运用之。例如,当叛乱的大臣邀请孔子去指导他们的政治运作时,孔子受到了诱惑,甚至打算接受邀请。孔子并不完全赞同这种叛臣的行为,但他为自己辩护说,假如拒绝了这种邀请,就有可能失去一个缓解人民苦难的机会。有了这样的根据之后,你还情愿保持个人的操守吗?这是个真正的难题。马克斯·韦伯指出:“世界上没有一种伦理学能避开以下问题:许许多多以‘善’为目的而取得成就的例子毗邻着这样的事实,即:人们必须情愿为使用受到道德怀疑的手段或者至少是有此危险的手段而付出代价,并且有可能面对某种不适当的结果,或者甚至可能是罪恶的结果。从世界上的非道德的行为能被做出定断之时起,一定程度上合乎道德之善的目的就合乎道德地为危险的手段及其衍生物‘做辩护’了。” [613]
孔子认识到,个人肯定会不断地面对这些难题,而这些难题每一次都有一定程度的独特性,因为从未有过两次一样的情势。直到今天,这种认识依然存留于中国的法律之中。法国法学家让·埃斯卡拉(Jean Escarra)在他的名为《公正的中国人》的书中指出,中国的法律程序基本上仍然是儒家式的。他说,中国的判案“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调节表面上很严厉的(法定的)惩罚,这种调节所运用的是我们可以描述为相当仁慈的、相当‘个人化’的东西。这种情形证明了中国刑法作者的真才实学。他们以其绝对的精妙和精密,创造了所有各种各样的刑事理论,从对犯罪动机的诡辩分析,到……同犯、宽恕、情有可原的环境、惯犯的罪行、犯罪的累积,等等”。 [614] 甚至是中国的法庭都知道,对个人来说,道德并不仅仅是使他的行为与一套严厉而固定的规则保持一致的问题。
既然孔子哲学把那么多的责任留给了个人,那么,除非他把教育人们的心灵和加强人们的品格当作他的首要任务,否则就会一无所成。在品格的培养中,典范的力量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像礼、道和义则是有助于人们进行自律的另一些原则。一个遵循中庸之道的人可能会犯错误,但他不会像走极端的人那样犯很严重的错误。孔子也认为,修养品格的结果不应该使一个人变得过分圆滑,以至于遮蔽了人的基本的刚毅精神,因为这种精神才是道德品格的真实基础。 [615]
甚至一个人的仁慈表现也应该用理性来调节。倔强的弟子宰予有一次对孔子说:“如果一个人是真有德行的话,即使你告诉他有个人掉在井里,我认为他也应该马上跟着下去(搭救)的。”孔子答复道:“你为什么这样想呢?你完全可能使用某种手法让一位君子下到井里去,但他不会不假思索地那样去做。他可以被欺骗,但不会被当成大傻瓜似的受到愚弄。” [616]
总之,在孔子看来,德行和真理并不是我们可以自感安全地休息于其中的安乐窝。确切来讲,它们是一些我们必须不断向它们奔走的目标。孔子说:“学习,就好像是在追随着一个人,你不仅无法超过他,还唯恐他把你甩掉。” [617] 这并不是说生命总是狂热的,也不是说人的内心总是焦躁不安的。相反,这场竞赛并不总是迅急的,也不是像那种最没有耐心的探寻者一样,总是在一刻不停地寻找他们所要搜寻的对象。通过教育和自律,并持守着中庸之道,我们可以从迷茫和不安达到沉静和自由。只要我们活着,我们真正拥有的种种道德力量就要担负着把它们运用到实际生活之中的相应义务,并在每种新的具体情势下做出选择,而这种情势是存在于向我们敞开着的各种行动路线之间的。孔子对此具有清醒的认识:“如果一个人不去不断地自问‘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拿他怎么办才好。” [618]
第十章 改革者
在差不多与孔子同时代,而又对政治思想有过详尽论述的思想家当中,最有名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以,西方学者就自然而然地拿他们的思想作标准,与表述在《论语》中的孔子的政治哲学相比较。这种比较的第一项结果容易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孔子的思想相对来讲是简单的和缺乏系统性的。这种看法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公允地讲,我们必须牢记双方之间的一些重要区别。
最明显的区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给我们留下了内容详尽的政论文章,而从孔子那里,我们只能得到一些零散的句子或段落。同样重要的另一项区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国家构想为小城邦,在《法律篇》中,柏拉图把它限定在5040户人家之内。 [619] 然而,孔子构想的国家至少统括全中国,而“中国”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又难以厘清的问题。再说,希腊政治的多样性允许当时的思想家利用广泛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经验,这包括君主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而孔子只了解中国的封建国家以及由于它的衰败所引发的政治现象。最后的,也可能是最有意义的一条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仅探讨了实际存在的和可以付诸实践的国家,也探讨了理想的国家。而在孔子那里,我们很少看到他在纯理论的层面上探讨国家问题。孔子几乎总是讨论政治改革。他相信,改革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我们看到了孔子希望改革的现状,这就是:普通人民深受压迫,几乎没有任何权力;统治者任意奴役大众,而大众的反抗方式只能是举行偶尔的但却无效的起义。统治阶级成员自身也是普遍的无法无天和不间断的战争厮杀的受害者。国君和他们的权臣是世袭的贵族家世的后代,除了一些罕见的例外,他们最终都成为这些家族普遍性的颓废堕落的牺牲品,而这些有权有势、生活奢侈的家族,都是父子相传了许多代的。他们只需要一代接一代地尽力培养两种长处:战争中的勇猛和搞阴谋的技巧。结果就造成了这样一个没有人关心人的尊严和人的幸福的世界,因为这些都是需要平心静气地深思熟虑后才能获得的。
面对这种状况,孔子深感不安。他决定献身于造就一个更好的世界。这是为什么呢?孔子拥有不同于他的周遭之人所抱的理想。同时,孔子也有他的思想,这是他赖以改变世界的手段。那么,孔子的理想和思想的源泉是什么呢?
从古到今,一般人总是认为孔子仅仅是在寻求复兴古人之道,并劝告时人回归到讲究道德的“先王”之道上去。孔子有两次确确实实地指出,古人是他的思想源泉,并且还用现在与过去的比较来蔑视现在。 [620] 然而,当孔子以嘲笑的口吻讲到当时的管理政府的官员时,一定程度上他只是在谴责不允许他推行改革措施的那些人,这是需要我们牢记的一点。
孔子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强调传统价值的人。还有柏拉图,尽管他也有诸如男人应该共同拥有孩子、妇女和财富之类的革新主张,但他还是宣称:“除邪恶之外,任何变革都是所有事情中最危险的。”柏拉图还说,立法者必须寻求一条牢固树立“崇敬古人”的道路。 [621] 在古代中国,崇敬古人是很普通的。董叔平指出,根据他对商朝甲骨文的研究,有意识地效仿过去的实际做法在孔子出生500多年前就已存在了。 [622] 后来,当相对野蛮的周邦国灭亡了商朝并取代其统治时,周人明确宣布了他们的意图,即遵从其“前代圣明之王”的习惯,并且还认为商朝之所以灭国就是因为它停止了“使用往古之道(古训)”。 [623] 遵从传统的重要性在《书》、《诗》和金文中屡被强调。 [624] 在中国古代,时尚就是尚古。
从这样的大的时代背景来看,孔子显然没有盲目地献身于传统。相反,他认识到了人类制度要有变化和发展,并且只要这些变化是合乎时宜和能被常识所认可的,他就积极地发动和接受。不过,孔子的这种态度和做法晚到汉代才被儒者认识到。 [625] 孔子说:“周朝的长处就是能够回头审察前两个朝代的经验。他的文化多么丰富啊!我遵从周朝。” [626] 很难想见孔子会去赞许一种仅仅依据传统做法的路线。孔子有11次被问到了政府应该如何行事(问政),他以传统习惯作答的只有一次。在这个场合,孔子说:“使用夏朝的历法、商朝有威严的马车和周朝讲究礼仪的帽子。” [627] 然而,孔子在此并不仅仅是劝告遵从古人,而是做出了一种实用性的选择,因为这种实用性是会被每个朝代所遵从的。这是很有特色的。它说明孔子不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崇古者,而是一个有所选择的传统主义者。
每当渴望良好的昔日时,人们只不过是缅怀那些时日的好的方面,这种想法是人之常情。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否真的如同康有为所认定的,孔子故意把他的新思想归之于古人(托古改制),以造成一种别有用心的骗局呢?我认为这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因为,与后来问世的以及那些可疑的著作中所塑造的孔子相比,《论语》中的孔子谈到古人之处是极少的。孔子也没有企图为他自己最具革命性的思想寻求传统的支持。尽管孔子在某一场合认为古代的一种观念(非常可能)相对来讲是新的, [628] 但这并不能当作孔子有意地布置骗局的证据,而此类做法显然有悖于孔子清晰表述过的有关原则。
孟子说,孔子的学说继承了古代帝王尧、舜和禹的思想。 [629] 一般认为,这些古代圣王大约是在西元前22世纪在位的。这种说法最终变成了儒家的正统思想,并且通常的主张是,孔子试图复兴这些早期帝王的“黄金时代”。可是,《论语》却并不怎么支持这种说法。孔子确实盛赞这些先王,但他并没有像孟子后来所写的那样,认为效仿先王以便实现完美的政治是历史过程的唯一的必然性。事实上,与明显地完成于后代的著作相比,《论语》很少提及这些帝王。
对于上述观点,我们拥有相当充足的证据。在本世纪,中国的学者们发现,尧、舜、禹都是上古传说中的人物。 [630] 在早于孔子的任何书籍和金文中均未提到过尧和舜。《诗》和《书》中提到了禹, [631] 而金文则认为他是个耕作之神。 [632] 根据记载,大禹疏通了几条大河,排干了大地的积水,使人们可以居住和耕作。因此,人们把大禹与“粟之王”后稷相联系,而后稷则是周朝王族的神秘的奠基者。 [633] 但是,正是《论语》最早提到了作为帝王的大禹,而尧和舜的名字也是首次在《论语》中才出现。
事实上,这些上古人物的故事大半是在孔子时代之后发展起来的。逐渐地,这些传说中的帝王被当成了所有儒家美德的原始模型。有一种值得怀疑的说法是:孔子创造了这些人物。如果这些人物是孔子创造的,我们应该会看到孔子要对他们大说特说,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孔子的时代,有关这些上古帝王的传说才出现不久,所以,孔子不可能从尧、舜、禹那里获得他的思想来源。如果说尧、舜、禹从孔子那里得到了他们的思想,这恐怕才是更近乎真情的说法。 [634]
孔子自称是周文王的文化继承人, [635] 而周文王是周朝创立者周武王的父亲。在《论语》里的意思有些含糊的一章中,孔子也曾表示,周文王的(另一个)儿子周公(旦)是他的思想灵感的来源。 [636] 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中国的传统说法就把周公看作是儒家思想的来源,有时甚至是儒学的奠基者,尽管事实上他要比孔子早500多年。 [637] 在《诗》、金文特别是《书》中,有大量早期周朝统治者的材料,《书》中的某些部分似乎是出自周公本人之手。在某些方面,这些文献显示出了与孔子思想的相似性,这是相当令人惊讶的。
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我们知道周人是相对原始粗鄙的野蛮人,他们蚕食了比他们更有文化素养的商朝邻人,并用武力将中国北部的大片土地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所以,他们的统治必然是相当粗鄙的。最早的周朝统治者们肯定是一些极有才能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物才可能在征服了广大土地的大胆事业中取得成功。在他们之中,特别有才能的是周公。当周公掌握了摄政者的大权时,周人刚刚赢得的版图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威胁。然而,7年之后,周公把一个稳固的帝国交给了他的皇侄(周成王)。总的说来,这些人是开明的。然而,尽管应该把那些本属于他们的东西给予他们,但我们也不必把他们讲说过的所有的人道主义的言辞都看作是出于真情。
周部落的首领们并没有管理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所必需的经验和机构(比如交通和金融体系等)。他们灭亡了商朝之后,把大部分疆土分封给了他们的亲戚和在征服中建立功勋的其他部落首领。周朝廷允许受封者(诸侯)在其领地内进行程度相当之大的自治,同时要求他们保持各自领地内的安宁以及在必要时出兵帮助周天子进行征伐。另外,按照周天子的规定,诸侯们也要向朝廷缴纳一定数量的贡品。这实际上就是封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朝廷把掌握着要塞驻军的诸侯颇为策略地分散在整个帝国。
不过,早期的周王们也是足够精明的,他们认识到,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不能像在打天下时那样纯粹用武力统治国家。商朝遗民举行的一次大叛乱更突出了这个事实。所以,周人进行了精心的宣传,给他们的征伐和统治制造了正当理由。像多半征服者一样,尽管他们是使用暴力才夺得了天下,但现在却返回头来谴责使用暴力。周人宣称,他们当初动用武力只是服从上天的要求,无疑是非常不情愿的和不得已的。根据他们的说法,实际上正是上天不断地审查世俗君主的行为。如果某个君主已经邪恶得不可救药,上天就会给那个该当受命建立新王朝的人颁下命令(天命)。作为上天的仆人,周统治者这才用武力征服了商朝,以表示对天命的服从。 [638]
那么,什么样的“邪恶”才会使一个君主必然倒台呢?周人特别强调的是没有适时地举行祭神,以及酗酒等行为。在商王的种种罪行中,周公还列举了一项:不好好地对待人民。 [639]
在周人反复进行的政治宣传中,周朝的君主才是真正的“有德者”。可是,这种说法并未告诉我们多少东西,除非我们知道了它的具体意指。在西方,有一个被认为是古代美德之真正楷模的罗马人,他被西塞罗(Cicero)誉为“勇敢而可敬的马库斯·卡托(Marcus Cato)”。 [640] 然而,根据蒲鲁塔克(Plutarch)的记载,卡托在每次欢娱之后,都要提着皮鞭走到他的奴隶中间,亲自“鞭打粗心的仆人或厨师”。 [641] 毫无疑问,早期周朝的许多“有德行”的贵族也在严酷地压迫普通民众。但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他们作为新近征服者的地位是那样地不牢靠,以至于他们受到了某种刺激,想使自己变得很吸引人,并以此作为一种对于新政权的保护性措施。周公特别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在一些可能是由他撰写并流传后世的文献中,他反复强调了以下事情的重要性,这些事情是:在断案中要公正甚至宽怀,宽容地对待人民,以及不要压迫无依无靠者和孤寡之人。 [642]
这使人想起了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大帝要求其臣下所作的誓言,他要求他们有义务“不侵扰亦不背叛神圣教会,或者是寡妇、孤儿和陌生人,视皇帝陛下为被指定的……所有这些人的保护者和辩护人”。 [643] 像周公一样,查理曼大帝也试图在一块广大而又联系松散的领土上巩固他的统治。所以,每当出现这种情形时,统治者们进行政治宣传的动机都是人道主义和政策策略的结合。就这样,上述两个当权者都变成了传奇人物,而且深刻影响了他们身后的历史。
在这种思想和历史进程的影响之下,古代中国人逐渐把理想的天子看成是管家之类的人物,而一位好天子的试金石是他能否给人民带来福祉。既然周朝征服者为使自己的天子头衔更加合法,从而声称他们取代了一个压迫人民的王朝,那么,公正和仁慈就成为此后的每个天子的义务。随着这种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每个当权者必须把他的职位看成是神圣的责任和艰巨的义务,换句话说,这就是当权者的最高行为准则。尽管我们大量看到的是几乎普遍存在的背叛道义而不是遵守原则,不过,当权者的实际行为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政治思想领域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至高无上的政治行为准则。孔子会很方便地从这一准则中找到对他的政治事业有用处的东西。尽管这一准则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正像人们对待耶稣的学说一样,这一准则还是被普遍地认为正好是对孔子学说的支持,而这样的支持是不会从其他的途径得到的。
孔子通常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倡导者。许多学者深信,孔子正在寻求复兴周朝早期的封建制度。这种看法主要是与一位学者(秦朝的博士)的说法有关,这位学者据推测是位儒生。在孔子去世266年后,这位学者责怪秦始皇没有给皇亲国戚和功臣名将分封土地。 [644] 但是,这位学者的主张根本不是孔子的学说,他建议给某些人封官的理由仅有一个,即他们是贵族的后代。事实上,在那些被有鉴定力的学者们认定的《论语》的可靠部分中,并没有倡导封建主义的痕迹。 [645] 当然,孔子也从未直接谴责过封建主义。然而,孔子确实希望对于实际政治进行很彻底的变革,他的这种激进主张与封建秩序几乎没有什么相似性可言。
要想知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政府类型是很容易的。我们只要翻一翻《共和国》、《法律篇》和《政治学》这些著述,他们会用自己的话告诉我们。但是,关于孔子,我们却没有这样的文献,而只能把《论语》中的零散资料分类整理,以便得出结论。也许孔子曾对他的弟子们描绘过一幅他的理想国的蓝图,但却并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只能把这些零散的资料拼在一起,尽力制成一幅相对完整的图画。
既然孔子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远不尽如人意,他就会自然而然地认定,一个完善之国应该具有他的世界所明显缺乏的东西,即:全体人民将享受和平、安全和富裕。孔子虽然十分看重和平,但他并不是个反对一切战争的绥靖主义者。然而,不必要的战争的确有悖于他的原则。毫无疑问,他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战争实质上就是自相残杀,更是整体性的天下无道的一个方面,所以,如果孔子倡导的政治改革能够成功的话,战争将会自动消失。
“子贡问如何管理政府。夫子回答说:‘一个有效的政府应该有充足的粮食、足够的武备和普通人民对它的信任。’子贡说:‘假如三项中的一项不得不被除去的话,会是哪一项呢?’夫子说:‘武备。’‘那么,余下两项中的哪一项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舍去的呢?’夫子回答说:‘那就把粮食舍去吧。因为,自古以来,所有的人都有一死。但是,如果人民对政府不信任,国家就不能成立。’” [646]
孔子最后一句的表述是极其重要的。它并不是说一个政府为了自保就应该饿死它的人民,因为那是荒唐的和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它的真正含义是,统治者不应该为了经济利益而过分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他的人民,还要以“为了人民本身的利益”为借口,认为人民太愚昧以至于认识不到这一点。当然,孔子的话语表达了以下的更重要的主张:国家的存在是一项协作性的事业,所有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必须共同理解其目的、享受其福利。
对于现代人来说,认识到这样的原则是轻而易举的。可是,在孔子的时代,要达到这种认识却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正如历史上所昭示的一样。孔子时代的世袭贵族很少主动表述他们的思想观点,只是“颠覆性”的儒学使他们不得不进行防御的时候,他们才被迫发展出一种完整的哲学。西元前3世纪,作为韩国公族后裔的韩非子能言善辩地谴责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君主和臣民有着基本一致的利益。在韩非子看来,爱君如父的想法是愚蠢的。父亲希望保护他的儿子,但君主却“在战争时期使他的人民丧命,而在和平时期则耗尽他们的劳力”。 [647] 根据韩非子的观点,人民是愚味的,当权者根本不必关注大众的利益。明智的君主不需要仁爱和公正,因为这些东西会导致无序。君主必须长久保持其财富和权力,因为所有的臣民都想着杀死他们的君主并取而代之。所以,君主不应该相信任何人,而只能持续不断地严厉监督所有的人。甚至君主的首要大臣也不应被授予太大的权力,而是要使他们对国君保持敬畏。韩非子的结论是,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必定造福于民的有序和良好的政府。 [648]
这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为支持这一理论,韩非子还引用了许多例证。但孔子想到的却是别的。孔子拒绝承认人人互相为敌的状况是人类不可避免的。相反,他认为人们应像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以至于“四海之内,所有的人都是兄弟” [649] 。确实,家庭之内要有秩序,甚至要有纪律,但是,促使人们遵守规矩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能够产生共同目的的、进行合作的积极愿望。所以,它也是政府应该具备的。
“夫子说:‘如果以法令的手段导引人民,以惩罚的手段维持秩序,人民便会仅仅是寻求躲避惩罚,而没有任何道德责任感。但是,如果用德行(包括告诫和典范)引导他们,并依靠礼来维护秩序,那么,人民将会感受到他们的道德责任,并去主动端正自己。’” [650] 这是孔子政治哲学的基础。没有消极的惩罚,只有积极的典范;没有让人民不去做什么的严厉规定,只有让他们应该去做什么的说服教育;没有用恐吓来统治的强权国家,只有一个协作性的共同富强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相互理解和善良意志。在这一点上,孔子与最现代的民主理论是一致的。林赛写道:“一个民主社会的成立或崩溃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够相互理解,这种相互理解就是,每个人都把别人而不是把自己当作目的。” [651]
每一种政治哲学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它的创作者所处的政治环境。古希腊有大量的民主政治经验,但这并不总是幸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某些方面出现了民主政治的衰败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便对“纯”民主表示了严重保留意见的态度。 [652] 另一方面,在古代中国,包括孔子在内,并没有人曾经梦想过如我们现在所知晓的民主政治的可能性。既然人民从未拥有过政治权力,政府的任何弊病就难以归罪于人民。孔子坚决站在人民一边,严厉谴责他们的剥削者——世袭贵族,因为正是这些贵族们把现实中的问题都归咎于人民。孔子一再重申,如果在位者是善良的和称职的,人民就会效仿他们的行为,而任何剧烈的惩罚也就没有必要了。 [653] 弟子曾子具有与孔子相似的气质和思想倾向。有个人被任命为执法官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曾子,而曾子则告诫那人说,作为执法官,当发现了一个普通人的犯罪证据时,不要为此而欢喜,而要感到悲哀和痛心,因为普通人的犯罪是以下事实造成,那就是:统治者“丢弃大道已经很久了”。 [654]
柏拉图被划归为哲学家之列,孔子则经常被称作宗教导师。然而,柏拉图却认为,与侍奉神灵相比较,“民间事务不值得过问”。 [655] 反倒是孔子对人民生活给予了极大的甚至是专门的关注。“樊迟问德行。夫子说:‘就是去爱人。’他又问知识。夫子说:‘就是去认识人。’” [656] 因为由普通人所构成的人的大多数受到了严重压迫,所以,孔子的主要愿望便是改革政府,使人民的生活安宁幸福。可以说,孔子把他的最高赞誉留给了善待人民的统治者。 [657]
孔子不是不知道这样的道理:如果人民仍旧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之中,任何其他改革都是无益的。当他被问到准备为大众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时,孔子回答道:“使他们富裕起来。” [658] 对于巨大的财富和拥有它们的人,孔子表现出的是轻蔑甚至是敌意。 [659] 孔子责怪发了财的弟子,无论他们是自己致富还是帮助他人敛财。他说:“君子帮助的是那些生计匮乏之人,而不是使富人更富有。” [660] 我们已经看到过了,当弟子冉求着手增加对人民的税收,以便为季氏积累更多的财富时,孔子就不承认他是弟子了。
许多政论家都主张,富人会在一定程度上比穷人对政府有更大的影响。 [661] 可是,孔子没有这种念头。在古代中国,商业无足轻重,致富的主要方式就是做官和收税。当权者要想发大财,必须得额外征税。这样,孔子就会自然地认为,要想非常富有,就得是个压迫者。孔子不是共产主义者。他认为统治者也有权生存,但却不是去过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如果他们能尽其职责,就应该得到适合其地位的生活享受。如果他们照顾到了人民的利益,人们是不会吝惜给他们以适合其地位的消费的。但是,如果他们做出了与上述要求相反的行为,他们就是吸血鬼。“夫子说……‘如果一个国家是依据大道来治理的,一贫如洗和处境低微就是一种耻辱;如果这个国家的所作所为不是依据大道的,那么,令人耻辱的就是富有和做官。’” [662]
孔子主张,人民一旦脱离了贫穷,就应该接受教育。 [663] 我们已经看到,实际上,孔子至少倡导了某种全民教育。他曾宣布,无论是多么贫贱的人,只要来向他寻求真理,他都全力以赴地帮助其解决难题。孔子从未拒绝过一个学生,他也因此而深感自豪。孔子把学生接收下来,训练他们以从政之艺。只要他们是有才智的和勤奋刻苦的,孔子并不在乎他们的出身和贫富状况。 [664]
就这样,依靠着倡导一定程度的全民教育,以及对那些有抱负的平民“君子”进行教育的计划,孔子向世袭贵族垄断下的政治秩序发动了最终的致命一击。我们这些视普及教育为理所当然的人很难认识到这是怎样的一场革命。在西欧思想领域,德莱尔·伯恩斯(C. Delisle Burns)说过:“教育的普及在大约1850年以前很难开始。在此前的世纪里,它被认为只对统治阶级才是有用的……” [665] 孔子确实是培养弟子从政的,但他所接受并加以培养的是相对来说出身贫贱的穷人,这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是具有破坏性的。 [666] 这一点也被一位英国牧师认识到了,此人就是J. 特威斯特大师(Reverend J. Twist),他在1822年撰写了一本名为《教育穷人的政策》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他警告说:“贫民阶层有一种荒谬的观念,认为他们与上层社会有同等的资格,同样拥有获得和增进知识的权利。这种看法可能会导致对公众和平的威胁,这正如某些革命狂热者有意图地教导人民说:是人的原因,而不是耶和华的意志,才使人民劳作和受穷。” [667]
孔子教育学说的革命性质并不为他的同时代人所欣赏,或者他们可能还认为这太不现实,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只是在知识的“毒素”被作了不可忽视的传播之后,我们才看到了对它的危险性的谴责。道家著作《老子》(当今多半学者认为明显完成于孔子时代之后) [668] 的作者宣称:“人民难于治理的原因是,他们知道得太多了。” [669] 法家的韩非子断言,在他的时代,太多的应该用于经济生产的时间完全被浪费在了学习上,这应归罪于孔子和其他人的有害的榜样。为矫正此种弊端,韩非子重申,应该销毁文献典籍。 [670]
当孔子在其有生之年大讲特讲其改革方略之时,显然并没有人为此而感到惴惴不安。孔子从未像孟子那样,直言压迫性的统治者应该被处死或者农民与帝王之间没有禀赋方面的不同。 [671] 如果孔子这样去做,他的整个改革运动极有可能会在很好地开展之前就被制止了。孔子依靠着某种程度的机智老练而打下了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孟子才有可能在一个世纪之后大胆放言而不受惩罚。这其中确实有一个机智策略的问题。孔子曾发表意见说,当一个人生活在腐败政府之下时,他应该准备一有机会就大胆行动。但是,因为言语本身不能矫正外界状况,所以,他在言语之时,还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小心谨慎。 [672]
然而,孔子并不总是谨小慎微的。在任何情况下,孔子都不想放弃他的基本信念,这个信念就是:就其本身而言,每个人都具有伟大的和本质上的平等的价值。孔子曾把弟子子路称赞为这样的一个人,他“穿着破烂的麻布袍子,能与身着轻裘的人并肩而立,却没有丝毫的羞耻之感”。 [673] 孟子引述孔子的话说,如果他的主张和行为是不正当的,即使面对的是最卑贱之人,他也将害怕与之争斗,“但是,如果反躬自问,认为自己是正当的,那么,即使是直面千百万人,也要勇往直前”。 [674] 孔子也同样宣布说,大臣自己的良心要比他的君主的命令具有更高的权威。 [675] 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重要区别是道德。尽管伟人并不多见,但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伟人。人生的真正价值与出身、财富或地位毫无关系,它依靠的是人的行为,亦即依靠他自己。
孔子是不会同意《独立宣言》中“所有人创而平等”的主张的。但他会同意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的主张,即:人“在他们的权利方面是平等的”。孔子认为他的一个弟子适合于登上君位,尽管这位弟子不是国君的儿子,并且还受到了某种家世阴影的不利影响。但孔子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位弟子是有德行和有才能的。 [676] 孔子也坚持认为,所有的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限制他们受教育的只是每个人的才智和勤奋程度。这种主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既然孔子认为政府的官职应该直接依据德行和才能来任命,那么,平等教育就意味着,在得到和提高社会和政治地位方面,人们有着几乎不受限制的平等机会。
孔子显然是站在人民一边的。孔子从未像西塞罗那样用轻蔑的口气讲述过“无知的民众”之类的话语。 [677] 不过,孔子的确认为人民是无知的,因为那时的大众实际上就是那样。既然人民确实无知,孔子就从未建议过把政府交与大众之手。孔子不怎么相信多数人判断的正确性,也不太相信世袭贵族判断的正确性,他认为这些人都需要进行教育。 [678] 孔子曾说:“普通人可以促使他们遵循适当的行动路线,但不必让他们理解。”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个有些含糊的表述时,必须指出另一项表述,在此表述中,孔子倡导说,要以大道教育普通人,并以此作为改进政治运作的手段。 [679]
在某些方面,孔子实际上是把普通人的常识作为他的判断标准。我们在上一章已经看到,孔子认为并没有关于真理的恒定权威。在科学上也没有这样的权威。然而,有一种荒谬的说法认为,所有的人在科学方面都是平等的。这就等于是说,任何人都能稳健地管理一个化学实验室或一所医院。其实,在科学方面,只有受过适当教育的人才会是称职的,尽管任何正常的和有才智的人都有接受此种教育的能力。实际上,孔子就是坚持了这样的思想。他保证接收任何一个有才智的学生。无论他们的社会背景如何,孔子都要把他们教育得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但是,孔子并不依赖任何神的启示或任何特殊权威的陈述,以确保他的观点被学生所接受。像科学家一样,孔子相信,通过诉诸人们的理性,他会使学生们信服的。这就是《论语》中内容有些含糊的一章的意思。在这一章中,孔子认为,普通人就是标准,依照这一标准,人们的行为的正确与否可以得到检验。 [680]
孔子所构想的最高的政治之善是人的幸福。这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并且很不同于仅仅使人们得到福利。最残暴的君王也可能声称,并且甚至是虔诚地相信,他们的统治是无所不至地关怀人民之福利的。比如说,西元前3世纪的专制君主、秦朝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曾使得数以千计的人被迫死于劳役,以建造大型宫殿和巨大的防御工事。然而,秦始皇在一项个人声言中却向人们郑重宣告,他是“圣人的化身。……为政事不懈操劳。……所以,所有的人都受益于圣人的神圣的仁慈”。 [681] 法家韩非子也认为,人民通常太愚蠢了,以至于不能弄明白这样的君主赐与他们的利益。 [682]
当然,所谓政府给人民带来福利的主张可以意味着任何事情。但是,幸福却是别样东西。“叶公问如何治理政府,夫子说:‘当一个良好的政府出现之时,近处的人会感到幸福,远处的人也会赶来。’”在另外一次,孔子说,当别国的人民打听到一个真正良好的政府时,他们是那样渴望在这个政府的治下生活,以至于会“背上他们的孩子赶来”。 [683] 这种观点的重要旨趣是,它们是让普通百姓,而不是其他人,来判断什么是好的政府,什么是坏的政府。人们可以被迫遵守秩序和从事生产,但却不能被迫感到幸福,就好像不能强迫一匹马低头饮水一样。只有依照人民的标准而臻至良好的政府,才会使他们感到幸福。
这样一来,我们必须进一步探究,当孔子讲到普通人民时,他指的是非贵族的全体人民吗?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古希腊的民主政治被人数众多的奴隶阶级的存在给严重毁损了。可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勉强接受了当时的现状,即一些人仅仅是另一些人的“工具”。 [684] 这样一来,对我们眼下的探究而言,重要的是去看看孔子是否也这样做了。
在任何真正的孔子本人的表述中,既未提到奴隶,也未提到奴隶制。这显然是说,或者孔子认为奴隶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以至于不需要予以评说;或者是在他的时代奴隶的数量极少,以至于奴隶制度相对来讲是不重要的。很清楚,后者是正确的解释。我们有证据证明,在孔子时代之前和之中是有奴隶的,但却是少量的和零星的。韦慕廷(C. Martin Wilbur)在其《中国西汉奴隶制》的研究中说,中国的奴隶制在汉代之前只是个“不充分的和不发达的体系”。他估计说,汉代的奴隶不足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在此之前的时代可能更少一些。 [685]
可是,这并不能肯定地说,奴隶之外的其余的人都是完全自由的。有许多证据说明,当时的劳动大众总的来说酷似于农奴的身份。在那个时代,几乎无法制止掌握权力的统治者役使他们的臣民。如果我们相信《左传》和《国语》的记载,与臣民们的日常生活相关的许多方面都受到了政府的非常严格的管制。在某些情形下,即使是高级大臣在都城都没有自己的固定房舍,而是要依照国君的意志搬来搬去。 [686] 普通百姓的居处和做工的地方都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如果他们不遵守,就会受到惩罚。毫无疑问,这些后来的著作对事实所作的详细说明和呈现出的人民大众受管制的情形比实际情况更有计划,也更严密。到了周朝后期(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人物开始主张对人民严格编户。事实上,坚持“返回到古代道路上去(复古道)”的主张的,正是那些被称作革新者的法家人物,而不是儒者。也正是为了反对强制性的管制和赞成较高程度的人身自由,孔子才发起了他的战斗。
现在,我们看到了孔子想要的东西。为了取代世袭贵族的专横统治,孔子主张应该让最有德行和最有才能的人依据全体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统治。为了替代一个恃强凌弱的掠夺性的社会,孔子希望看到一个人人为全体人的利益而尽其所能的合作性的社会。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是,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理想呢?
最近出版了一部书,作者是郭沫若,这是一位具有“左”派倾向的杰出的中国学者。此书所描述的孔子不仅仅是人民卫士,而且是武装革命的鼓动者。可是,郭氏为证明他的后一种观点而提出的证据明显是脆弱的。郭氏显然是要依靠着他的热情,为孔子洗清自古以来的错误的指责,即指责孔子是他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的工具。但是,郭氏走到了相反的极端。 [687] 孔子的确曾有两次受到了诱惑,打算加入到背叛其上司的那伙人之中。但是,即使孔子真的那样做了,并且反叛者也获得了成功,这也不过是以一套世袭贵族政治取代了另一套。那种强有力地和完全彻底地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的真正的革命,在孔子的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贵族的叛乱司空见惯。普通百姓有时也会对他们的压迫者奋起一击,但这种暴动从未有意要改变当时的政治制度。老百姓并不知道如何管理政府,他们甚至不认为他们有权利或者有能力进行这种管理。只是在儒家教育实施了几个世纪之后,贫穷出身之人才开始坐上王位。要说孔子打算用武力去寻求贯彻他的理想,那将是既不切实际,亦有忤他的本性的。
当然,孔子也没有倡导使用选举的手段。这不仅是因为在人民之中完全缺乏有关的必要教育,更重要的是,在古代中国并没有人曾想到过或听到过选举的做法,然而,政治选举在古希腊却是众所周知的。孔子不得不通过与占据权位的世袭贵族相往还而开展他的工作,推行他的政治改革。所以,尽管孔子并不喜欢世袭制,但他并没有别的选择。
有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孔子是在寻求恢复名义上在位的周天子的权力,但是,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并没有提出什么有力的相关证据。在《论语》中,孔子从未认真提到过在位的天子。周天子早已成了傀儡,也缺乏政治威力和品格力量。孔子在世期间,几个觊觎王位者之间就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有时是流血的斗争。 [688] 也许部分地正因如此,孔子才认为,完全可以说华夏中国是“没有君主(无君)”的。 [689] 要去企图恢复不能胜任的周氏家系的权力,对任何人都无好处,并且孔子也没有这种想法。 [690] 相反,孔子(像后来的孟子一样)认为,还不如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权威机构去取代周天子的位置。这个意思无疑表达在他所说的希望重新建立“东周”的想法之中。 [691] 孔子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治理得非常好,全体人民就会被强有力地吸引住,以至于他的统治者不久就会控制全国。
为了实现这样的计划,孔子希望找到一个真正有德有智的统治者。尽管孔子从未像孟子那样直截了当地表述革命权力的学说, [692] 但他却一再澄清说,仅仅是具有家族继承权的人尚无权进行统治,而任何不称其职的统治者也没有资格在位。“夫子说:‘如果一个人能端正自己,管理政府还有什么难处呢?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能把握自己,他又怎么去管理别人呢?’” [693] 既然他那个时代的多半当权者都明显缺乏自控,这样的论述就显得特别尖锐有力。
没有必要去列举孔子认为的在位者应该具备的品质,确切来讲,这样的品质就是理想儒生的品质。其中之一使人想起柏拉图的话:“除非哲学家是王者,或者这个世界上的王公贵戚具有哲学的精神和力量,并且政治的高尚性和哲学的智慧合而为一。……诸城市将永远不会停止它们的邪恶——不,人类都不会,正如我所认为的……”但是,柏拉图也承认,这实际上是一项非常难于完成的政治事务。 [694] 至于孔子呢,在周游列国中花费了好多年的时间找寻一个愿意学习他的哲学的君主,但最终却毫无成果。这使他逐渐认识到,世界的整个命运不能依赖如此微弱的希望。因此,孔子就在一些论述中把君主贬斥到了事实上的“在位而不谋其政”的地步。孔子说:“人们认为,大舜是无所作为的,但他不是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吗?他仅仅是端正自己并待在君主应该待的位置上而已。” [695]
可是,君主的“无为”并非意味着政府中所有的人都是无所事事的。确切来讲,孔子所谓的“无为”的国君是把所有的具体政务留给了他的大臣们。当然,这样的君主首先得选择贤臣良辅。有一次,当孔子说国君应该“提拔正直的人”时,一位弟子没弄明白,于是,子夏引述了传统的说法作为例证。子夏说:“大舜从众人中挑选,提拔了皋陶(他成为有德行和受人欢迎的大臣),于是,邪恶者便逃之夭夭了。” [696] 在《论语》中,孔子反复强调了完全以德行和才能作基础来挑选和提拔官员的重要性。 [697] 因此,尽管在孔子死后的几个世纪才采用了受人欢迎的科举取仕制的最早的形式,但是,正是孔子最早构想了这个制度及其目标。同时,孔子在这方面的具体论述肯定有助于这一制度的实际建立。
所以,根据孔子的观点,政府管理的着重点不在于君主而在于他的大臣。保罗·莱茵伯格(Paul M. A. Linebarger)描述了中华民国建立之前中国的政治理论,他写道:“对于日常工作,皇帝本人并不掌管,但他选拔和监督他的大臣们,让他们去做……” [698] 人们逐渐认为,这种观点的形成可能主要是受到了孔子思想的影响。 [699] 然而,法家韩非子却强烈反对这种观点。韩非子断言,精明的君主不会把权力交给大臣。他说,有头脑的君主不会任用精明的大臣,因为他们会欺骗君主;君主也不会有纯粹的大臣,因为大臣们还会被别人所蒙骗。 [700]
很可能是孔子的个人经历影响了中国政治理论的这个基本方面。如果孔子找到了一个意气相投的国君,准备用他的权力将孔子思想付诸实施,那么,孔子就不会急于主张下放君主的权力。可是,孔子并未成功地在国君中找到同情的倾听者,相反,更多的倾听者正是大臣,或者是可能成为大臣的那些人。因此,孔子才要抬高大臣的地位,甚至认为国君从善并不比拥有贤臣更重要。 [701]
孔子也指派给了大臣一个更高的负有道德责任的地位。因为大臣应该受教于大道, [702] 必须具有不总是从命于世袭君主的品质。因此,尽管大臣应该忠于其主,但孔子问道:“忠诚不正是应该导致对其所忠之对象的教诲吗?” [703] 当子路问如何事奉君主时,“夫子说:‘不要欺骗他,但在必要时要当面反对他’”。孔子本人实践了这种率直的说话方法,他告诉鲁定公说,如果国君的政策很糟但却没有人站出来反对的话,这种不讲原则的政治足以毁掉一个国家。 [704]
总之,尽管一位大臣应该是忠诚的,但他一定不是和事佬,他的终极的忠诚不应该给予任何个人,而应该给予大道。可是,这并不是说孔子不尊重任何政府机构,相反,他痛惜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并谴责那些篡夺其上司的权力和特权的人们。 [705] 从这一点来看,有时孔子会被看作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不遗余力地维护现状。但是,即使在今天,“一个民主国家的各种权力机构,不是并且也不可能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民主作风自动发挥其作用。……一个等级严明的组织结构是确保民主政府发挥其技术效能的最有效的方式”。 [706] 孔子希望彻底改革他那时的政府。但是,孔子也认识到,在成功地改革了政府之后,必须要做的就是要求那些政府官员应当服从他们的称职的上司。“君主一定得是君主,臣下一定得是臣下,父、子亦然。” [707]
孔子的这个政治体系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从终极意义上讲,良好的政府依然要依赖君主,因为他们掌握着最高权力,而且,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并没有办法迫使他们选贤任能。孔子事实上也没有办法强迫他们。所以,孔子只得去影响要做大臣的年轻人(可能他们还会成为君主),而影响的途径,则是教育以及来自受过教育的公众所形成的舆论的社会压力。在孔子的时代,这场运动正处在它的早期,还没有收到多少实际成效,但在接下去的几个世纪的历程中,它终于形成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因为儒生偏偏是对书本感兴趣的人,所以,他们就逐渐几乎达到了对文献和教育的垄断地步。他们写下了(并且为了宣传的目的而修改了)大部分的历史记载,并最终获得了教导大部分王公贵戚的地位。
说来说去,讨论的着重点又回到了儒者个人和作为个人的儒者。由于受到政治权力运作和实际改革功效的阻碍,孔子转而通过教育(促进其社会改革的唯一可行的手段)培养这样的人——儒生。儒生先是学生,在后世的许多情形下,他们又成为教师,如果环境令人满意,他们还会成为政府官员。孔子认为,儒家君子并不是只通一业的专门人才, [708] 而是精通所有政治事务的全面手。所以,他们就像种子一样扎根于任何令人满意的土壤里,并利用任何有效的手段推动孔子所倡导的社会改革运动。
孔子认为,一个合格的儒家学者应该只在一个良好的政府里或准备听从自己指导的政府里任职,但是,“当国家无道时,他就收拾起他的原则,并保存在怀中(卷而怀之)”。 [709] 以这项原则为基础,一些后儒(尽管不是全部)就很顺当地假定说,孔子主张一个人不要在任何可能的危险情势下采取行动,以免使他个人或他的平静生活遭受风险。可是,这既不能与孔子的“见到正义之事不要怯懦(见义不为,无勇也)”的主张相一致,也不能与《论语》中其他相关章节所阐述的观点相一致。 [710] 事实上,正如汤用彤指出的,这项儒家原则的主旨是拒绝与政治上的腐化堕落相妥协。 [711] 为此,儒者有时会舍弃他们的生命。
柏拉图完美地表达了孔子所说的思想。在《共和国》中,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述说道,真正的哲学家,如果发现自己处在邪恶环境中时,“就不会加入到他的同胞的邪恶活动之中,但他也不能独自一人去阻止他们所有人的残暴行径。所以,当看到这一切时,他会不与他的国家或他的朋友发生关系。经过反思,在既不能为他自己也不能为别人做任何好事时,他宁可抛弃其生命。他保持缄默,只管走他自己的路。……他是心满意足的,即使只为他自己的生命而活着,并且不沾染邪恶和不义。他怀着光明的希望,平平安安地、心安理得地死去。
“是的,阿德马修斯(Adeimantus)说,在去世之前他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
“一件伟大的工作——是的。但还不是最伟大的,除非他找到了适合于他的国度。因为在一个适合于他的国度里,他会有更大的收获,并成为他的国家以及他自己的拯救者”。 [712]
这样一来,注意力就集中在了个人身上,所以,儒家所强调的管理政府的着重点就落在了官员的个人品格上而不是管理机制上。荀子说:“我只听到过修养品格的方法,从未听到过如何管理国家的方法。” [713] 前者如果达到了要求,就完全可以成为后者的准备。当然,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这种倾向的夸张在西方却没有受到重视。西方人要严格考查一名被提名的法官候选人是否拥有必备的法律知识,但却不太在意他是否具有智慧和仁慈,以及心胸宽广。这种儒家式的态度是整个中国习俗的一部分。这种一直坚持至今的习俗就是:以个人的而不是非个人的方法(某些社会学家称之为“私下协定”)处理问题,认为个人比职位更重要,个人比组织更重要。另一方面,法家则几乎完全强调政府的管理系统和法律。在法家人物看来,如果法律行之有效,管理井然有秩,政府基本上就会自行运作。在此,我们很显然地就碰到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问题,他说:“令人烦恼的问题是,到底是人治好还是法治好。” [714] 公平地说,韩非子(可能是法家思想家中最有才华者)也并没有头脑简单地认为,即使君主本人没有才智和能力,国家政治依然会取得成功。但他深信,君主应该掌握某种类似于对个人能力和创造力的垄断权之类的东西(“术”)。 [715] 可是,有一个方面总是被人们忽视的,那就是,尽管孔子并不太看重法律,认为法律是一套目的在于强迫人们向善的规则,并相信政府管理应该依靠善良官员的创造性的判断,但是,他也并不认为这样的官员们可以依据随心所欲的怪念头进行管理。相反,孔子要求他们一定要接受道德原则和政治管理方面的彻底的教育,以便得到公众的信任。也就是说,他们只有被证明完全消化了这种教育,才会被任用。孔子要求他们不要超出大道的范围,一切都要以良心和公众舆论为准绳。儒学的确有一种反法意识,但它从来都不主张无法。 [716] 莱茵伯格在论述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其中占优势的是儒家体系)时说道:“在中国,每个人都了解这个既成的传统,而士大夫们也要与普通百姓一样完全服从于这个传统。” [717]
亚里士多德以为,“法律规则比任何个人主张更可取”。不过,他也说:“与成文法相比,习惯法更有分量,并且关乎更重要的东西。而且,一个人可以成为比成文法更可靠的统治者,但却比不上习惯法可靠。” [718] 这非常接近于孔子的思想,但它把社会的导向留给了习惯,却是不十分理想的。
根据林赛的看法,古希腊人并未在“斯多噶学派时代之前获得一种完全普及的最高自然法的概念,即:自然法是应该绝对服从的。……古希腊也缺乏这样的法律概念,即:法律是指导法官断案的普遍原则,而法官则既公布法律又发展法律”。 [719] 可是,这种原则在罗马人的《侨民法》(或《国际法》)——它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发展中是很重要的——中被找到了,而西塞罗则把它定义为“建立在所有民族之中的自然理性之法”。 [720] 斯多噶派建立在人类平等基础之上的自然法概念起着相同的作用。 [721] 这些观念与儒家的道、礼、义等概念的相似性是那样地明显,以至于毋需对它们进行讨论。
我们现在准备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孔子所倡导的政治改革,是不是,或者说在多大程度,可以被说成是“民主的”。这个问题并不荒唐。但是,孔子倡导的政治改革与我们当代社会所具有的民主制政治不是也不可能是同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赶快认清这一点,就可能把它弄成荒唐的问题。当代民主政治产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在不可忽视的程度上,它的基础是近代以来不断扩展的人类经验和诸如科学的、物理的、社会的以及工业化等方面的现代发明。 [722] 然而,正是由于孔子与现代民主政治倡导者之间所处环境的巨大不同,他们的思想之间的任何的一致之处才显得特别令人感兴趣。
欲问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否是民主的,须问民主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在很久以前就写道:“民主……肯定不止一种形式。” [723] 而这个难题自他的时代以来并未变得更简单些。就这个论题进行写作的人太多了,并且写得也太好了,以至于难以概括他们的论点。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E. Merriam)所表述的“民主制度的主要假定(前提)”如下:
1.重视个人的基本尊严,根据友爱的而不是有等级差别的原则去保护和培养人的个性,还要消除政治特权,因为这种特权的基础是对人的差别的没有根据的或过分的强调。
2.努力不懈地实现人类的完善,并对这种努力充满信心。
3.有这样一种假定,认为公共财富基本上应该为大众所获得,并且尽可能迅速地散布到整个社会,而不会产生太多的耽搁或太悬殊的差别。
4.归根到底,最理想的状况是,根据群众的利益决定社会的发展方向、制定基本的政策,以及确定一个做出这种决定的固定程序,以保证政策的正当性。
5.对以下可能性表现出信心,即:为了完成有意识的社会变革,应该通过说服教育获得公众的同意,而不是依靠暴力强迫人们顺从。 [724]
很清楚,其中的四点(不包括第四点),基本上与孔子的思想一致,并且这种一致性在一定情形下还是相当地突出的。余下的那一点(即第四点)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实际上不得不通过选举来实现,而孔子显然从未构想过任何由人民群众控制政府的方式。不过,我们早已指出过,选举的观念在古代中国从来不为人所知晓。其实,当1791年的法国宪法在法国革命中期被颁布之时,就有人“以无产阶级是文盲以及选举的作用决定于接受教育和拥有经验的程度为理由来反对普选权”。 [725] 那么,在西元前500年,孔子并未提出中国的政权应该移交给当时的农民,这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任何这样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空想的和无益的。不过,一个与此相关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孔子是否认为,在教育及其相关条件都很理想的情形下,人民群众应该掌握政权。这很难作答。很可能答案是否定性的。但是,让我们先来排列一下与孔子的政治观点相等同的一项表述,也就是把我们已经述说过的孔子的政治思想汇集在一处(这项工作是孔子从未做过的)。那么,孔子显然认为:
政府的适宜目标是全体人民的福利和幸福。
只有当这个国家由那些最有政治才能的人管理时,此一目标才会达到。
政府官员的管理才能与他们的出身、财富或社会地位并无必然联系,它完全决定于品格和知识。
品格和知识产生于适宜的教育。
为使最有天资的人变成有用的人才,应该广泛普及教育。
政府应该由这样的人进行管理:他们选自全体人口,通过适宜的教育证明他们会造福于大多数人。
这样的观点显然与全体人民应该掌权的说法并不相同。但它却是在说,每个人都应该有显示其是否有能力参与掌权和管理的机会,而一旦证明某人有此能力,他就将不仅被允许而且被鼓励参与政府的管理。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贵族体制,但不是由出身好、有财富的贵族,而是由有德行、有能力的贵族去管理政府。从民主政治的观点来看,孔子的这个体制有这样的不足之处,即:没有那种使大多数有能力的人不得不被任用的机制,但这是由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的无法逃避的事实。更重要的一个不足之处是,孔子的体制也提供不了让全体人民影响政府的真正有效的途径。的确,孔子所说的政府应该使人民幸福的原则只给了民众一个含糊的“原则上的”否决权,但是,在那个时代,孔子所做的也只能是如此而已。
另一方面,某些民主的坚定信仰者却害怕我们在“大众”政府的方向上走得太远。正是这种惧怕使伊曼努尔·康德谴责了他所谓的民主政治,并且在同一篇论文中他又宣称:“每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都应该是共和政体的。” [726] 阿兰·哈特斯利在他的《民主政治简史》中说:“让人民参与政府的行政和司法管理是以对人民主权学说的极端解释为基础的。政府机构一定要由它们的实际工作成效来评价,那种认为每个人在地方政府中都有不能取消的分享权(而不考虑其妥当性)的理论产生了不胜任的政府管理和政策缺乏连续性的不良后果。行政和司法机构的公开选举忽视了对有关特殊才能的要求。而对于这种特殊才能,一般民众明显没有资格进行品评。” [727]
其他当政者则强调说,民主体制并不能取消政府机构中有技术专长者和有实际才能者的工作。林赛论述道:“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那些有权力和有专业技能的人既要为社会工作,还要受到既无权力又无知识的普通人的约束。……适当地讲,民主政体并不是由人民进行管理的。” [728] 梅里亚姆的评论是:“根本不能消除特殊才能,相反,民主政治可以把最高奖赏授与有才能者,彻底摒弃身无一能者。” [729] 阿瑟·霍尔库姆认为,事实上,“现代民主制是一种贵族政治”,在其中,“许多职位,包括最重要的职位,都是根据无关乎财产和名望的专业特长来任命的”。“进一步扩展选贤任能的体系和在总体上较好地完成国家的发展蓝图,就意味着吸引聪慧的和有才能的人进入公共机构,使整个政府系统的权力得到发展。这是真正的贵族政治的本质。” [730] 如果孔子真的是在倡导贵族政治,那在一定意义上与上述主张就很相似了。
政府的管理形式和机制的重要性从来都不应该被轻视。不过,人类经验也雄辩地证明,它们并不比作为它们的基础并产生出它们的精神和哲学更重要。当然,任何把真理视为恒定的和绝对的实体的哲学都很容易偏向于政治独裁主义的方向,而与此相反的一种信仰却是朝向于政治民主的,这种信仰就是:真理(或者至少是对真理的理解)是在一个不断发展或展开的过程之中,并且所有的人都可以宣布分享对它的创造或发现。
显而易见,如果真理是恒定的和绝对的,并且社会中的某些成员可以拥有它,那么,这些拥有者就会认为,强迫没有知识的人与这种真理取得一致是正当的,而且认为,这种强求是对无知者的实实在在的仁慈。但是,如果没有人能绝对地确定真理为何物,并且进而为获得真理的努力寻求一个有张力的和经验积累的进程,那么,每个社会成员就有了参与探求真理的范围,在此范围中,他们以一种协作性的(亦即民主的)努力去决定政治生活应该具有的目的和方法。
众所周知,现代极权国家与哲学绝对主义之间有着密切的姻亲关系。德莱尔·伯恩评论道,在独裁统治的教育体系中,“教授给人们的东西已经被提前肯定为是由一贯正确的领袖们所揭示的真理……” [731] 赫尔曼·芬纳写道,独裁体制“要使人们相信,或者无论如何都要宣称,社会最终的完美形态已经被一个人揭示了出来……”但他又说,在民主体制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意识,那就是认为,完善的政治形态尚未找到,并且一直需要在一个永远发展着的世界中去寻找……” [732]
在这样的辩论中,孔子的立场显然不是在绝对主义一边,而是在不断寻求真理的主张一边。孔子确实相信他拥有的是一个终将取得成效的政治方案,而一些民主改革的现代支持者也不乏自信。不过,孔子给予他的弟子的既不是真理的表述也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标准,而是使他们自己到达真理彼岸的训练。“夫子说:‘人能扩展大道,但是,大道不能(自己去)扩展人。’” [733]
孔子的这种主张明显是强调了个人价值的重要性,这使得孔子有资格坚定地站立于民主阵营之中。很少的极权主义者会对这种主张犹豫不决,即:为了善的利益而把恶的东西置诸死地,但孔子对此拒绝接受。他没有断然谴责一切死刑,而是宁愿相信,如果政治和教育井然有序,就将不需要死刑。 [734] 极权主义理论坚持认为,个人自身无权反对国家,而是必须完全服从国家。芬纳说:“专制国家消除其党派成员个人良心上的责任,并尽力麻醉或催眠人的心灵。在民主国家里,个人良知可以完全地负责,并被有动力的观点的冲击波所翻新、所困扰。” [735] 孔子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不断地自问‘怎么办’,我就不知道拿他怎么办了。” [736]
理想地说来,民主体制下的国家是一个人们自我管理的社会,所以,具有民主精神的人就自然而然地应该认为“国家对强力的使用是其内在的缺憾而不是其光荣”。 [737] 有一些人,比如托马斯·佩因(Thomas Paine)就认为:“较完善的文明是,政府少有用武之地,因为政府更多的责任是管理自己的份内事务和约束自己的行为。” [738] 有很多证据表明这就是孔子的观点。孔子曾评说道:“在判案上我并不比别人能力强。但是,有必要做出努力,使得在国家事务中不出现诉讼案件。” [739]
这种状况显然将是理想之境,并且只有在人们彻底浸透了积极的理想时才能出现。民主政治与极权主义相对立的关键之处是:在极权政治中,许多人是带着锻造束缚他们社会的锁链的狂热激情而工作;而在民主政治中,太多的人有相互不同的朝向,以至于并未意识到他们的自由。民主政治需要持续性,并且总是要求全体人民对民主原则的正当性要有一定的理解和信心,同时,那些在民主政治活动中起带头作用的人也需要对民主的理想富有真实的热情。
孔子的了不起的长处就是他能够激发这样的热情。孔子允许他的追随者们保持他们的良知,并且坚持认为他们在良知面前一定不要让步,同时,孔子也要求他们在其他所有事情上都要为人类服务。不论是财富,还是世俗的荣誉,甚至生命本身,如果它们不能与大道保持一致,就不应该被享有。以下这个信条具有一种宗教的热诚:“如果一个人在早晨听到了大道,他可以毫无遗憾地在晚上死去。” [740] 对于大道,仅仅有理智上的默认是不够的。孔子说:“仅仅知道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而喜爱它的人又不如能够从中得到快乐的人。” [741]
可是,孔子的思想并不是宗教,这是它的长处。一旦人类的知识获得长足发展,那么,这些信仰——致力于特殊的形而上学理论,严格的信条,或者关于人性和宇宙的反思——的基础就一定会受到冲击。但是,孔子的思想中并没有多少绝对主义的东西,同时,孔子思想也力求接近普通人的需求和人类的同情心。这一事实使孔子思想的基本原则在经历了文化体系的一系列整体革命之后依然能够生存下来。
在中世纪,“教会的存在和威望使得社会免遭极权主义之害,阻止了极权国家的产生,并保护了自由。……而教会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在社会中维持一个与国家相抗衡的组织”。 [742] 德莱尔·伯恩甚至认为,在今天,“可能在某个地方有某种带有‘宗教命令’性质的东西,这种东西与某些人相结合,这些人对以下事情更有热情,即:倡导普遍之善,或者是为了普遍之善而工作。……这是一种非强迫性地传播思想和新习俗的群体”。 [743] 儒学在中国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按:胡说八道,基督教会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组织,而不是各地的小国家。】
可是,儒家却从未被组织起来过。它没有首领,没有行动纲领,也没有组织机构;它从未被摧毁,也未被完全控制。历史上是有过对孔子的祭祀,但那是国家行为,不是儒家的事情。
从外表上看去,儒学的最初形成和发展是孔子弟子们对孔子的个人魅力所做出的自发的反应。孔子希望弟子们忠实于大道,但他们对他个人的敬服从来都不是纪律约束所致,用孟子的话来说,弟子们是因为“内心的一种喜悦而真诚地服从(中心悦而诚服)”孔子的。 [744] 即使是在政府管理方面,孔子也相信自愿的合作胜过规则的规定。所以,孔子虽然没有建立任何形式的组织,但却有意识地发起了一场运动。
这场运动是要制造一种力量,用以抗衡世袭的并且是占有统治地位的军事贵族,因为他们掌握了垄断性的政治权力和特权。像中世纪欧洲的“武侠”骑士一样,许多这样的贵族视战争为儿戏,看重匹夫之勇,把杀人当作他们的人生目的。 [745] 孔子并不是古代中国唯一的一个这样去做的人,即:谴责贵族所看重的毁坏性而不是建设性的成就。《国语》记载了一位官员愤怒的讲话,他告诉他的主人说,他对国家一生忠心耿耿,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可是,他从未因此而受到赏识;但他现在却被赏识了,原因就是他在战斗中杀了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因为仅在一刹那间我就变成了你所说的‘我一定得奖赏你’的那种疯子了。” [746]
孔子不是个绥靖主义者,他并没有完全取消贵族的习惯或传统。他自己还射箭,并称赞身体锻炼的好处。晚到汉代,儒家学者们还都是射手。但是,孔子确实在努力寻求改变贵族政体。他的最终目标是,使这种政体的存在以美德而不是以继承权为基础,还要使其中的成员献身于工作而不是掠夺。
尽管战争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孔子还是明确认为这是一种罪恶。孔子并不关注军旅之事,除非它能用于正义之事。同时,孔子在任何情况下都认为身体之勇远在道德勇气之下。总的来说,孔子不考虑勇力的功绩和武力的使用,他把赞誉留给了那些能够真正地造福于人类的人们。 [747]
孔子的这种情感必然招致那些恃强凌弱的贵族们的侮弄。在儒学发展的最早时期,很可能正是这些贵族不无嘲弄地把那些依靠学识而不是勇力的人们称之为“儒”,即“懦弱之人”。 [748] 孔子只在《论语》的一章中使用过“儒”这个字,但它似乎只是慢慢地才被后来所称谓的“儒”者集群本身所接受,尽管这个集群之外的人早就在用这个字来称呼这个集群了。 [749] 可是,直到西元前3世纪,儒生才引以为荣地使用它,而它的原意却可能已被忘记了。
正是这群“懦弱者”才是孔子的希望所在。在自己的时代,孔子为他们做了很多,点燃了他们心中热情的火焰;这团火焰沿着一条不断的路线,直至传递到了我们手中。孔子不能使弟子们得到世袭的权力位置,但他却巧妙地使他们适合于“君子”之名,从此以后,“君子”之名更通常地是指饱学而文雅之人而不是指贵族出身之人。孔子称他们为“士”并要求他们(以令人惊异的成功的标准)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并献身于普遍之善。为了长远的和平目的,人们通常要保留战争的争斗,但孔子给予他们的武器是笔,盾牌是书。孔子也给了他们一种使命:勇往直前并取代权力中心的强权色彩,以人类的名义和利益掌管世界。
然而,在孔子去世之时,成功的希望对他来讲是渺不可及的。
注释
[1] 《左传·昭公七年》。《左传》这段记载在开头处有确切的编年,但《史记·孔子世家》却给弄错了。讲到孔子家系的这次对话发生在孔子30岁时,此时的孔子尚未成名,然而,这个对话却预言了孔子未来的远大前程。崔述认为这个世系有一些疑点(崔述,卷一)。此世系把孔子说成是宋公的后人,而宋公的上世是被废黜的商朝天子的继承人——微子。这可能是有根据的,但根据的不是事实,而是这样一种观念:孔子应该做天子。早在《墨子》中,一位儒生就断言,在孔子的有生之年,如果有一位圣人在位的话,孔子就会登上王位(《墨子·公孟》);而孟子则应人请求,解释了孔子为什么没有登上王位(《孟子·万章上》)。
——译按:根据相关记载,可以肯定孔子确实是商王帝乙的法定继承人微子的后人。虽然某些儒生据此事实而故意神化孔子,但这并不足以说明这一事实是不存在的。参阅拙著《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3—5页;《先师孔子》(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第3—16页)。
[2] 《春秋经》的《公羊传》和《穀梁传》上的日期是西元前552年,《史记》则是西元前551年。学者们为此曾长期争论,莫衷一是。因为西元前551年更常用,所以本书用此。
马伯乐(Henri Maspero)认为,孔子的生卒日期可能比现在普遍接受的西元前551—前479年要晚25年(马伯乐,455n.1)。但这是不可能的。孔子的生年可能有些疑问,但既然孔子弟子接续了一个不间断的传统,就没有理由不知道他的卒年。事实上,我们可以有充足的理由说,孔子卒于西元前479年的记载至少是接近了实际。比照《论语·宪问十四》及《春秋·哀公十四年》,孔子一生最后的事件可以确定在西元前481年。在与他一生有关的任何确实的材料中,再没有什么事件和人物可以把他的寿数延长到西元前479年以后。《孟子·滕文公上》说,孔子去世后,部分弟子在墓地守丧3年。而颇得季氏赏识的弟子冉求,在西元前481年后就未被提到参与公务,直到西元前472年(详见《左传》)。子贡(孟子说他守丧6年)直到西元前480年都是鲁国的主要外交官。此后,他就未被提及参与公务,尽管他在外交方面显然还有很高的声望,并且人们也很希望他去完成外交使命(详见《左传》)。这些事实都支持西元前479年的说法。如果说《左传》已被窜改,删去了弟子服丧期间参与公务的事例,那么,相反的证据也有,那就是弟子子羔(高柴)参加了西元前479年的一次外交会议(《左传·哀公十七年》)。下文还要提到,子羔并不是一位很被孔子看重的弟子(《论语·先进十一》“柴也愚”章和“子路使子羔为费宰”章),也不是一位很彻底的儒者(《左传·哀公十五年》)。
如果孔子卒于西元前479年,生于西元前551年,他便活了72岁(译按:应该是73岁)。根据种种理由,孔子很可能活到了这么大年纪。早在西元前498年,他的弟子子路就担任季氏宰的要职(《左传·定公十二年》)。《论语·为政第二》(孔子自谓“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认为孔子至少已活到了70岁(这可能不是确数),而总的来讲《论语》是把孔子刻画成了一位可尊敬的老人。所以,他可能就出生在西元前551年左右。
[3] 《孔子家语》(卷九)和《世家》都认定孔子之父名叫叔梁纥,这显然是认为这位叔梁纥与《左传·襄公十年》、《左传·襄公十七年》中的叔纥是同一人。可是,在这两个场合,《左传》(通常是以微不足道的借口提起孔子的名字)显然并没有明示叔纥就是孔子的父亲。那么,为什么在后来才认定了呢?原因可能简单得近乎荒唐。《论语·八佾第三》只把孔子之父记为“鄹(地之)人”,称孔子为“鄹人之子”,而《左传》提到的唯一的“鄹人”就是叔纥。对那些在早期文献中仔细搜寻有关孔子的片断材料的人来说,这无疑已是足够的了。
[4] 见《论语·公冶长》首章,《论语·先进十一》“南容三复白圭”章、“颜渊死”章和《论语·季氏十六》“陈亢问于伯鱼”章。
[5] 崔,卷四。
[6] 不仅是我们不知道叔纥是孔子的父亲(见注 ),就是认为叔纥是鄹地大夫——大抵说他是邑宰的《孔子家语》(卷九)显然也没有适当的根据。唐朝的注释家孔颖达解释说,既然《左传》称“叔纥鄹人”,这就是说他是鄹地大夫(《左传注疏》卷三十一),这种说法并没有说服力。
——译按:孔颖达之说依据的是《左传》记事体例。另外,《左传》是记年体史书,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是接续不断的,而都是散记在诸多年份和事件之中,有关孔子的记载也无例外。所以,以《左传》中关于孔子生平的记载缺乏连续性而质疑这些记载的真实性,是不值得肯定的。而在这个问题上,顾氏显然失之于随意。
[7] 《论语·子罕第九》“大宰问”章。
[8] 《论语·颜渊十二》“颜渊死”章。
[9] 《国语》卷十五。
[10] 《论语·子张十九》。《左传·昭公十七年》讲的一个故事说,孔子26岁时曾求教于郯子,但这并不值得重视。《论语》和《孟子》均未谈到郯子,而我们很希望在这两部书中出现孔子的老师。《左传》的这项记载把郯子与玄鸟、龙,各种“云官”、“火官”和“鸟官”,还有“五雉”和“九扈”等联系起来,这都具有后世神话的特点。
——译按:《论语》和《孟子》没有记载的事情,未必就不是事实。特别是在孔子的生平和思想方面,《左传》和《国语》的记载应该与《论语》和《孟子》具有同样的价值。
[11] 《孟子·万章下》:“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译按:孔子的文化修养,特别是他在古典文献方面的高深素养,不可能在这种工作中获得。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具有大家族背景的社会成员,才有学习这方面知识、得到这些方面相关训练的机会。
[12] ——译按:《论语·子罕第九》:“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孔子讲“君子不多”,并非自责,又非自卑。孔子一生颇多得益于“少也贱”的磨砺。在孔子看来,艰苦的生活固然不一定造就伟才,但在一定条件下却有助于伟才的成长。所以,孔子称赞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论语·子罕第九》)而不以为耻的精神。
[13] ——译按:《论语·述而第七》:“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子罕第九》:“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
[14] 《论语·公冶长第五》:“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译按:孔子抨击的“佞”人,只是无原则的善辩之人。孔子并不是没有口才,他与子贡等人的区别是以什么样的原则指导口才的使用。
[15] 见本书第七章,原书页码第106页。
[16] ——译按:《论语·颜渊十二》:“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论语·宪问十四》:“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17] ——译按:《论语·子罕第九》:“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18] ——译按:这种结论稍嫌片面。事实上,孔子的收徒设教开始于30岁左右(详见拙作《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16—18页)。只是到了晚年,当客观上从政无望时,孔子才把全部精力集中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
[19] ——译按:在孔子之前和同时,郑国的邓析、晋国的叔向和鲁国的少正卯等人,都以收授弟子而闻名,但他们或是为了个人生计,或是为了表现个人才能,或是为了与某个当政者做政治抗衡,而并没有像孔子一样把教育作为一项事业和行业,更没有像孔子一样为教育本身规定社会责任和目标。
[20] 《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孔子33岁时,临终的孟氏首领孟僖子吩咐他的嗣子和另一个儿子求学于孔子,而他们后来也照此吩咐去做了。他们有时被认为是孔子的首批弟子。但这个故事有几方面的疑点。孟僖子吩咐之前,先讲述了孔子的高尚品质并概括了孔子的家世,说他是未继嗣的商朝天子(微子)的后代。而且,如果这兄弟二人(其中一人是后来有权势的孟氏家族的首领)早年做过孔子弟子,就应大力支持孔子,我们也盼望《论语》对此有记录。然而,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在《论语》中只出现过一次,也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是孔子弟子。(《论语·为政第二》、《论语·宪问十四》,南宫括和南容的身份最令人怀疑)
——译按:《左传·昭公七年》所言二人是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不过,顾氏的怀疑并不有力。据《左传》,此二人只是向孔子学礼,并没有像颜回等弟子那样长期求学于孔子,更谈不上是同道。孔子弟子如冉求等尚且不能在实际政治上全力支持孔子,遑论政治实权人物会有如此举动。另外,对于早期典籍,顾氏的态度也有问题。比如,对于《左传》中有关孔子的记载,不能随心所欲地此时相信这一处,彼时又怀疑另一处。对于《论语》,其中记载的事实固然大多可信,但并不能因此就下结论,凡是《论语》中没有记载的事件和人物都不可信;《论语》并不是孔子的“起居注”,而是在不断的散佚和增补中形成的。
[21] 据《左传·定公十二年》,西元前498年,作为季氏家宰的子路,在当时的鲁国内政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此时,孔子53岁。传统说法(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认为,子路比孔子小9岁,此时44岁,这与周遭情形是一致的。另一位弟子曾皙,即弟子曾参的父亲(《孟子·离娄上》)也一定属于这个较早的集群。在《孟子·尽心下》中与曾皙一起被提到的另两位弟子(琴张和牧皮)在《论语》中未出现,而曾皙自己也只出现过一次(《论语·先进十一》)。很可能是《论语》无意中遗漏了一些孔子的早期学生。
——译按:这可能是因为《论语》乃孔子后期弟子以及后期弟子集辑而成,所以,前期弟子中之名微者、早逝者或离门者均少有记载。如上所言,《论语》的史料和思想价值虽然无可比拟,但它既不是孔子的“起居注”,也不是“孔门全书”。
[22] 钱穆,第56—62页。
[23] 《左传·哀公十一年》。
[24] 详见《左传·哀公十四年》。
[25] 《论语·颜渊十二》:“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无)。’”
[26] 《论语·雍也第六》:“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先进十一》:“颜渊死,子哭之恸。……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
[27] 《论语·雍也第六》:“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28] 《墨子》(2),第238—239页。
——译按:《墨子·公孟》:子墨子曰:“姑学乎,吾将仕子。”
[29] 《论语·里仁第四》:“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宪问十四》:“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卫灵公十五》:“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泰伯第八》:“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30] 《论语·为政第二》:“子张学干禄。”
——译按:“干禄”只是从政的同义语,重点在于单纯地求取俸禄。大抵顾氏从译成英文的《论语》中看到“求取俸禄”之类译文,所以才把“干禄”的意义理解得较为狭窄了。
[31] 《论语·泰伯第八》:“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译按:此处“三年”,原非实指,乃泛言数年、多年。
[32] 有证据说明,一个特定家族的家“宰”的位置是独一无二的。见《左传·成公十七年》“施氏卜宰”、《左传·昭公八年》“立子良氏之宰”。
[33] 子路、冉求和公西华同时在孔子门下,他们未被任用时自认为他们的才能没有被赏识(详见《论语·先进十一》“侍坐”章)。孔子把子路和冉求推荐给季氏(《论语·雍也第六》“季康子问”章),此二人(非常可能是相继)得到了季氏家宰的职位。公西华曾出使齐国(《论语·雍也第六》“子华使于齐”章)。冉雍出生在一个有瑕疵的家庭,这妨碍了他的仕途(《论语·雍也第六》“子谓仲弓”章)。不过,孔子高度评价了他的才能(《论语·雍也第六》“雍也可使南面”章),而据说他也当上了季氏家宰(《论语·子路十三》“仲弓为季氏宰”)。没有孔子的帮助,他很难得到此位。
[34] 吉本,第564页。
[35] 《左传·定公九年》。根据《论语·阳货十七》首章,马伯乐认为孔子接受了“阳虎给的一个职位,并在(阳虎的夺权)阴谋失败后被认为做了有损名誉之事”(马伯乐,第456—457页)。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首先,《论语》此章以及《孟子·滕文公下》讲的都是阳货而不是阳虎;他们可能是同一人,但并不确实。其次,《孟子》没有提到孔子任职的问题,而《论语》此章也仅仅引用了孔子的话说:“吾将仕矣。”这根本没有说他已经做了,而是说在阳虎手下什么都还没做。最后,《左传》所述阳虎之所为明显不是孔子个人所喜欢的那类事情。阳虎是个以暴力恃强凌弱的阴谋家,《论语》和《孟子》都明示了孔子不想与阳货产生任何瓜葛。所以,孔子根本不可能是阳虎的同党。
——译按:一般认为,阳货和阳虎是同一个人,阳虎与孔子有过交往也是不争的事实。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家,都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没有政治上的往来是不可想象的。阳虎是篡权者,孔子是文化名人,阳虎想利用孔子也在情理之中。孔子虽然反对政治阴谋,反对僭越和篡权,但在政治上有时不免有幻想,甚至有幼稚的表现。在阳虎专权的情况下,孔子一时产生利用阳虎的想法也不奇怪。但是,无论有什么样的政治幻想和幼稚表现,孔子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刻把握住自己。所以,否定阳货和阳虎为一人,或否定孔子根本不会与阳虎相往来,并不见得是理解和描述孔子的恰当做法。
[36] 《左传·哀公二十四年》。
[37] 《左传·哀公十一年》。
[38] 《论语·先进十一》“子路使子羔为费宰”章。
——译按:似乎不足根据此章就说明子羔中止了在孔门的受教。顾氏又根据《左传》的记载(即弟子们为孔子守丧期间,子羔仍活跃在鲁国政治舞台),断言子羔背离师门,这似乎也同样是根据不足。
[39] 《左传·哀公十七年》。
[40] ——译按:《论语·先进十一》:“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并详见《左传·哀公十一年》、《左传·哀公十二年》。
[41] 《左传·哀公三年》。
[42] 《论语·雍也第六》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能否担当政府职位。这应早于子路担任季氏宰的时间,也就是不晚于西元前498年(《左传·定公十二年》)。
[43] 《论语·乡党第十》:“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
——译按:季康子送药给孔子,并不是当作普通礼物,而是孔子生病了。晚年孔子多病,但他又精通药理,所以才会没有服用季康子的馈药。
[44] 《论语·颜渊十二》:“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45] 《论语·乡党第十》:“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46] 《论语·雍也第六》:“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欤)?’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欤)?’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欤)?’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47] 《左传·定公十二年》:“仲由为季氏宰。”
[48] ——译按:《左传·定公十年》:“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子相。”这是西元前500年的记载,早于子路担任季氏宰的记载,顾氏却未予采信。同一典籍,同样明确的记载,却可以自由裁量信与不信,显然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49] 《左传·定公八年》。
[50] 《左传·定公九年》、《左传·哀公七年》。
[51] 《论语·阳货十七》:“公山弗扰以费畔(叛),召,子欲往。”
[52] ——译按:根据《左传》记载,孔子在西元前500年(定公十年)参与夹谷之会,公山弗扰在西元前498年叛乱失败,逃往齐国,孔子还指挥了这场平叛。所以,《论语》所记公山弗扰召孔子,至少当在西元前500年之前,而观本书叙述顺序,似乎是在子路担任季氏宰之后。这还是因为顾氏不相信孔子这一时期会在鲁国从政,也才有了孔子“年迈无力”之类的说法。
[53] 《论语·阳货十七》:“夫召我者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54]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这是偶发的冲动,并用大量精力试图证明这件事并未发生过。其中的一位是崔述,他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其时孔子为鲁国之司寇,根本不可能被叛者“召”(崔述,卷二)。这件事是真的,但是既然孔子担任过司寇一职非常值得怀疑,那么这个真实发生的事件就变成了进一步的证据,去否定孔子曾任司寇(无论何时何地)的说法。冯友兰相信《论语·阳货十七》描述的这个事件确实发生过[冯(7),第37—38页]。钱穆认为它可能发生在西元前502年或西元前501年,这与当前的考证完全一致(钱穆,第14—16页)。
——译按:如钱氏之考可被接受,则公山之召正发生在孔子仕鲁并任司寇之前。此时,孔子有从政的急迫,也与他后来担任司寇的事实不相矛盾。顾氏坚持认为孔子没有担任过鲁国的司寇,这一稍嫌独断的态度妨碍了他对孔子生平很多事情的认识和评价。
[55] 《左传·定公十年》。
[56] 《左传·定公十年》记载了“夹谷之会”时孔子对蛮夷之人(“莱人”)讲的一句话,“对于神灵是不吉利的(于神为不祥)”,这听上去并不像《论语》中的话语。如果说仅凭几句话就迫使强大而好战的齐国交还了它并不想交出的土地,那将是非常荒谬的。为康熙皇帝编写皇家版的《春秋》注释的学者们删去了这一节,并引述一些学者的意见,认为它是失实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五卷)。令人惊讶的是,《左传》并不多载孔子一生中的某段具体情节,而像这样的传奇或这样详细的描写亦无它例。显然,这件轶事是编撰好了之后插到原典之中的,正如本书刚刚引述的那样,以便给孔子记一大功,即《春秋》所提到的收回土地一事。
——译按:《春秋·定公十年》:“齐人来归郓、 、龟阴田。”《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载了孔子率众击退公山弗扰之叛军的事件,这与“夹谷之会”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并且也有细节描述。定公十三年正是西元前498年,而顾氏认定《左传》在这一年所记载的“仲由(子路)为季氏宰”是可信的。既然对子路的记载为可信,就没有理由怀疑在同一地方对孔子的记载。至于对“夹谷之会”的详细描述,类似的手法在《左传》中随处可见。不能说对其他事件的详细描述为可信,而对有关孔子的事件的如此叙述就不可信。在《左传》的记述中,以一句话使强敌退兵的故事随处可见。别人能做到的,孔子也有可能做到。
[57] 《墨子》(2),第209页。梅贻宝在《墨子·非儒》章写道:“此章结构和文体明显有别于(《墨子》的)其他章节。而历史日期和事实的混淆显示出它是较后时期写成的。”(同上,第200页)胡适也表示过对这一章的怀疑态度(胡适,第151页)。特别可疑的是提及孔子时称“孔某”(意即“某位孔先生acertain Mr. K' ung”),这是虔诚的儒生为避免使用孔子个人的名字而用的一种称谓。然而,早在《孟子》时尚未如此使用,尽管孟子是位良好的儒者。在攻击孔子时如此使用是很奇怪,这便明示出此章是后来加入原典中的。
——译按:即使《墨子》中的《非儒》篇是晚出之作,也不能证明其中的内容是失实的。事实上,《非儒》篇的写作目的是贬损孔子及儒家。依常情而论,要贬损孔子,更应该把孔子的社会地位说的低一些,而不应该把孔子抬高到司寇的高位。另外,顾氏对“孔某”的解释似乎不妥。“孔某”大抵为贬称,而不是讳称。孟子以后虔诚的儒生多矣,却未有一人公然称孔子为“孔某”,因为“孔子”才是尊称。倘用现代汉语讲,“孔某”即是“姓孔的那个人”或“姓孔的那家伙”之意。
[58] 《左传·定西元年》:“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为鲁司寇也,沟而合诸墓。”
——译按:因鲁昭公生前与季氏有过公开冲突,故鲁昭公遗体自国外运回后,季氏故意把它葬在鲁公墓地的墓道之南,而鲁国其余先公均葬在墓道之北。季氏的意图是明显的,即认为鲁昭公不称其职。孔子不同意季氏的做法,所以在担任司寇之后,就用一道沟把墓道南北之墓都围了起来。《左传》之所以在此提及孔子,是由鲁昭公之下葬引起的。书中一定要强调孔子为司寇,是因为以沟围墓地不可能是普通人办得到的。而既然此处已说明了孔子做鲁国司寇,到孔子担任司寇时,也就可以不用特别说明了。这是《左传》的体例,不应该因此而怀疑其记载的确切性。
[59] 《孟子·告子下》:“(孟子)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脱)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
——译按:季氏之所以对孔子“无礼”,主要是不满意孔子之政。从历史记载的角度看,对于《孟子》中记载的有关孔子生平事迹的内容,没有理由采纳这一条记载而否定另一条,否则会使一切陷入混乱之中。关于孔子做鲁国司寇的记载,主要典籍的说法是一致的,是不容置疑的。
[60] 译注:《孔子家语·刑政》:“造异服。”
[61] 这些个故事出现在《孔子家语》卷一和卷七,以及《荀子·宥坐》等。后者的材料明显出现在《荀子》中较为晚出的部分里,梁启超认为是汉代人编入的(见梁,第115页)。对于刑罚的看法,真正的儒家论述可见《论语·为政第二》“道(导)之以政”章,《论语·颜渊十二》“季康子患盗”章、“季康子问政章”以及《论语·子路十三》“善人为邦百年”章。对孔子处死少正卯之说法的反驳,见崔述,卷二。
——译按:《左传》中并未记载类似诛杀少正卯这样的事情,尽管这种事情也未必不可能发生。不能说因为后来的书籍增添了一些孔子任司寇后的所谓“政绩”,就全盘否定有关孔子做鲁国司寇的所有记载。
[62] 见马伯乐,第457页注[2]。《左传》只在襄公二十一年(前552)提到一次鲁国司寇的名字——臧武仲。尽管这个家族的首领后来不得不两次外逃,但他们的继承人依然被任用,而其家族也还是显赫的(详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传·哀公八年》、《左传·哀公二十四年》)。在缺乏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说这个家族的首领是继续担任司寇的。
——译按:《左传》中记载孔子做鲁国司寇就是顾氏所说的“相反的证据”。
[63] 《论语·子罕第九》:“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
[64] ——译按:在有关孔子生平的记载中,后人的认识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孔子生平中的有些事件,也许在今天看来事关重大,但在编辑《论语》的时代却是常识,不必大书特书。尽管如此,《论语·乡党第十》中所记述的孔子的言行,还是证明了孔子有过很高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拥有过政治权力并不意味着就有机会取得突出的政治成就。所以,顾氏否定孔子做鲁国司寇的论据总的来说并不充分,论证也欠周详,一定程度上正如认定孔子担任过此官职的看法一样。顾氏对有关孔子的许多事件的怀疑,深受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界疑古之风的影响,现在看来,这种态度并不十分可取,尽管他对孔子思想的许多论述相当深刻。
[65] 西元前498年之前,季康子问过孔子,这三位弟子是否适合从政(《论语·雍也》“季康子问”章),结果,子路在西元前498年做了季氏宰,而子贡则在西元前495年出席了一次外交盟会,并随后在季氏手下担任重要官职(《左传·定公十五年》)。《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冉求在西元前484年任季氏宰。《论语·先进十一》“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章以及《论语·季氏十六》“季氏将伐颛臾”章是说子路和冉求同仕季氏,这可能在子路随孔子出游之前,不晚于西元前493年。可是,必须指出,“季氏将伐颛臾”章的真实性是不能确定的。
——译按:顾氏此证多牵强之处。定公十五年,子贡只是回鲁国“观礼”,原非从政。况且其时孔子正在流亡,子贡只是被孔子派回观礼,随后又回到孔子身边,向孔子讲了观礼后的感想。冉求从政是在孔子流亡末期,也就是孔子年近70岁的时候,而子路在鲁国从政是孔子50多岁时。孔子流亡期间,子路一直伴随左右,到流亡末期才去卫国从政。所以,三位弟子同时从政,只能在孔子于西元前484年归鲁之后,且不在同一国。在孔子弟子从政时间的问题上,顾氏没有严格地区分孔子周游列国前后时期的不同,造成他不得不多方去说。
[66] 《论语·为政第二》:“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译按:孔子此语,讲在定公初年,此时,孔子40多岁,之后才有仕鲁为司寇之事。如上注所言,三位弟子咸仕时,孔子已是垂暮之人,别人不太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67] 《论语·子罕第九》:“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译按:虽然子贡有时并不完全遵从孔子的意见,但此语似乎并不是责备孔子,而是理解孔子、关心孔子,因为他也提到了“善贾”,不是随便卖掉。
[68] ——译注:《论语·颜渊十二》: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69] ——译按:如果认真研究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期的政绩,顾氏的这种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70] 公山弗扰邀请孔子的事件大抵发生在西元前502年,这一年,阳虎发动叛乱,而西元前498年公山弗扰便不得不逃离鲁国。这个邀请发出时,孔子的确几乎不可能在官位上。孟子说孔子在季桓子手下做事,而季桓子则死于西元前492年(《孟子·万章下》:“孔子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而且,《左传·哀公三年》说,这一年(西元前492年)孔子在陈国,想必是他已经开始周游列国了。另外一个不太可靠的记载说孔子在西元前500年左右从仕。就是在这一年,被编入《左传·定公十年》的一件非常可疑的轶事说,孔子协助鲁定公参加了“夹谷之会”。《穀梁传》卷十九则对这一件事有不同的说法。《公羊传》卷二十六(在一定程度上略去了这个故事,这就等于是否定了它)还认为孔子“对季氏取得了成功”(“行乎季孙”),这也许是意味着孔子先在西元前500年,然后又在西元前498年从政。
——译按:阳虎和公山弗扰的图谋进行了好多年。他们二人先后邀请孔子,肯定是在其叛乱的准备阶段。如果在叛乱公开之后再邀请孔子,孔子从政的心情再急迫,也不会与他们应对。所以,不能因为公山弗扰之邀就认为孔子不可能在西元前502年之后从政。另外,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顾氏显然是把孔子50岁之后四五年的从政经历(在鲁定公时代)与孔子晚年作为鲁国的咨政者(在鲁哀公时代)混为一谈了。
[71] 《论语·子路十三》:“冉子退朝。子曰:‘何晏(晚)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译按:此事显然发生在鲁哀公时代孔子晚年最后归鲁以后,与鲁定公时代孔子的为官不在同一时期。顾氏本书的许多事件考证,都未能注意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区别。
[72] 《论语·乡党第十》:“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因为这一章出现在《乡党篇》,韦利(Waley)和其他一些人就认为这讲的是“君子”的一般行为方式,而并不是专指孔子个人。但也有可能是,这一章像本篇的其他某些章节一样,一定指的是特殊的个人。
——译按:《论语》的最早版本(一传弟子所作)相当于现在前十篇的内容,《乡党篇》居末,显然是讲述孔子的日常行为。正因为《乡党篇》的内容与此前叙述孔子言论的篇章有所不同,才采取了不同的叙述方式,但若因此就认为是讲述君子的普遍行为方式,则明显是违背了弟子们编写《论语》的初衷。
[73] 《论语·先进十一》“颜渊死”章和《论语·宪问十四》“陈成子弑简公”章。
——译按:“从大夫后”大抵是一种委婉的自我认定身份的说法,并不表示官职的大小。
[74] 比较“从嬖大夫”,它被解释为“作为嬖大夫之一”,载《左传·昭公七年》及《左传注疏》卷四十四。
——译按:嬖大夫即下大夫。《左传·昭公十年》:“卿违,从大夫之位。”讲的是因罪由卿降位至大夫叫作“从大夫”。简言之,本身为大夫者,才可以称为“从大夫”。
[75] ——译按:季康子继其父季桓子执掌鲁国大权时,孔子早已周游在外。孔子被季康子请回鲁国时,已经68岁,体弱多病,且孔子弟子冉求身居季氏之宰,地位相当牢固。显然,此一时期的季康子客观上是不可实际任用孔子的。况且,也不能以这一时期孔子的不仕证明他一生无仕。传统上认为孔子的从政并担任鲁国司寇是在鲁定公和季桓子时代,即孔子50岁到55岁的五六年中。
[76] ——译按:其实,在传统的专制社会,某个官员权力的大小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官职,而主要在于他与当权者的关系是疏远还是亲密。如果鲁公和季孙当时都能信任孔子,孔子的权力便不会受到职位大小的限制。
[77] 如果我们认为,孔子首次从政是在鲁哀公时(这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形并未改变。只有《论语·宪问十四》“陈成子弑简公”章能使我们把时间确定在西元前481年(《左传·哀公十年》),但这对于我们现在的目的来讲是太迟了。而从孔子与鲁哀公的两次谈话(《论语·为政第二》、《论语·雍也第六》“哀公问”章)中,我们显然看不出他是鲁哀公的近臣。
[78] 《论语·八佾第三》、《论语·子路十三》“定公问”章。
——译按:顾氏此论,未免过拘。处在鲁定公当时的几近傀儡的地位,是不可能问孔子“患盗”、“民服”之类的不切实际的问题的。
[79] 《孟子·万章下》:“孔子之仕于鲁也……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
——译按:孟子此处只是强调了孔子对季桓子的态度,并不是说直接仕于季氏。当然,孟子这句话也表明,孔子仕鲁之时,正是季桓子掌权的时代。季桓子是权臣,掌握着鲁国的政治资源,鲁公根本不可能独立任命大臣。换句话说,任何像孔子那样的平民,要想在鲁国得到政治职位,没有季氏的同意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此意义上说孔子仕于季桓子也是可以的。但令孔子稍感安慰的是,至少在名义上季桓子还算是鲁公之臣。
[80] 《论语》未记载孔子与季桓子的任何谈话。
——译按:这几乎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论语》不可能记载孔子一生的所有事件,哪怕是现在认为的重大事件。在孔子仕鲁的问题上,顾氏是从结论出发找证据,而不是根据证明得出结论。顾氏首先认定孔子不可能在鲁国得到实职,然后看到《论语》中没有记载孔子与季桓子的交谈,就否定了孔子在季桓子时代从政的可能。但对于孔子与季桓子同时代的鲁定公的交谈,又认为交谈的内容不是君臣间的交流,从而再次否定孔子从政的可能。到了季康子和鲁哀公的时代,又认为季康子与孔子政见不同,不可能任用孔子。对于孔子与鲁哀公的交谈,又认为时间太晚,不足以说明孔子有时间从政。这些论断,都有推断性太强的毛病。
[81] 《公羊传·定公十二年》说是孔子作此劝告的。
[82] 《左传·定公十二年》载,在某一场合,当鲁公与“三家”首领被围攻时,孔子指挥士兵营救了他们。这是可疑的。孔子的名字令人怀疑地突然出现,而且这是唯一的一个场合,他甚至被描述为正在指挥军队。
——译按:如果孔子当时任司寇,指挥军队并不奇怪。《左传》并不是孔子的个人传记,不可能有始有终地记载孔子的从政经历。既然《左传》在同一处同时记载了子路和孔子的作为,似乎并没有太多的理由说对子路的记载为实,对孔子的记载为不实。况且,对子路的记载也是“突然出现”的。相反,《左传》记载孔子在定公十年参与“夹谷之会”,定公十二年指挥军队平息叛乱,对于《左传》体例来说,不是“突然出现”,而可以说是频繁出现了。顾氏此处对孔子出现在《左传》中的怀疑,似有鸡蛋里挑骨头的嫌疑,不值得提倡。
[83] 《论语·宪问十四》:“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
[84] ——译按:如前所言,顾氏在此又混淆了冉求从政的时间。子路任季桓子时的季氏宰,而冉求则任季康子时的季氏宰。根据《弟子传》,子路从政时40多岁,而此时的冉求不过20出头,很难想象他已经掌握大权。《论语·子路十三》又言“子适卫,冉有仆”,说明孔子周游之初,冉求亦随行。如果在此之前冉求已从政,他又怎么会辞职呢?
[85] 译按:所谓“懂得把黄油抹在面包的哪一面”乃西方熟语,指生活和选择的明智,顾氏在此当有揶揄冉求的意思。
[86] 对“事”的此种解释比一般的说法——“私事”,更完满一些。说见戴,卷十三。
——译按:“事”指日常行政事务,“政”指国家大政方针。
[87] 《论语·子路十三》:冉求退朝。子曰:“何晏(晚)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这种译法不太拘于原文。但我认为它准确地道出了原意。这段文字记载的事件通常认为是孔子周游列国返回鲁国后的事情。但孔子离开鲁国,是因为他不再幻想了,而他回来之后,他的劝告明显是不被理睬的,所以,在后期他不可能有希望过问任何已发生的重大事件。
——译按:根据上注,孔子出游之前,冉求不可能从政。而孔子晚年归鲁是季康子发出的邀请,咨询国事并不奇怪。况且,根据《左传》记载,季康子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推行新赋法时,多次派人征询孔子的意见,而此时的孔子已经68岁了。
[88] 《孟子·告子下》“淳于髡问”章:“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脱)冕而行。”
[89] 《论语·微子十八》“齐人归(馈)女乐”章,这是暗示齐国人送女乐让鲁公消遣,致使孔子辞职,因为齐国怕孔子把鲁国治理得太强盛。这类似于《论语·微子十八》中的大部分章节,几乎无疑是虚构的,这是孔子传奇的一部分。崔述指出,孟子没有在我们期望他提到的地方说到此事件,因之对它提出疑问(崔述,卷二)。
[90] 《庄子》卷二,第172页。
——译按:顾氏所据是英译本,大约是指《庄子·天地篇》中类似子贡与孔子的对话那样的篇章。
[91] 《论语·述而第七》“子在齐”章和《论语·颜渊十二》“齐景公问政”章。《孟子·万章下》:“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墨子(2),第206—209页。
——译按:顾氏所指,大约是《墨子·非儒篇下》“孔某之齐,见景公”之类的章节。
[92] 译按:孔子55岁时离开鲁国,齐景公在孔子61岁时死去,景公在与孔子的会见中自称“吾老矣”(《论语·微子十八》),所以,从时间上说,孔子未必就见不到齐景公。
[93] 《墨子》中有这样的两则故事,见《非儒篇》。它们出现在这本书的那部分不仅是明显的增补(见本书注 ),而且在其中的一则故事中,晏子讲给齐景公(卒于西元前490年)的楚国的一次叛乱却发生于西元前479年(《左传·哀公十六年》)。而《晏子春秋》讲到这些故事之一时又有一些不同看法。这本书也有几则晏子与孔子对峙的故事,或把他们当作同代之人(《晏子春秋》卷七),这在编年上是有问题的。《左传》经常提及晏子,他最后出现在西元前516年,此时孔子只有35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另一方面,照《晏子春秋》的证据,这些事件发生时孔子已经名声在外。事实上,到孔子成名时,晏子可能已经去世了。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轶事不能被看作是史实。整部《晏子春秋》的完成日期是难于确定的,人们一般认为它要晚于孔子在世的时间。见《伪书》,第607—609页。《论语·微子十八》“齐景公待孔子”章几乎无价值可言。孔子从未与鲁国“三家”的首领平起平坐过,无论如何齐景公不会为了孔子而提到“三家”。如同《论语·微子十八》的其余篇章一样,这无疑是传奇之言。
——译按:《论语·公冶长第五》:“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孔子30多岁时在齐国待过六七年,很可能与晏子有过交往,不宜因为《晏子春秋》的时间错乱而断然否定这一点。
[94] 《史记》卷五,第304—310页。
——译按:此处所说《史记》卷数,当是英译本。
[95] 《论语·卫灵公十五》。《孟子·万章下》:“孔子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
[96] 《孟子·滕文公下》:“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
[97] 由于《论语·先进十一》“从我于陈蔡”章的记载,有人认为至少有10位弟子随行,其中包括最杰出的几位。但是,显然有两个不相关联的说法可以相互证实。《论语·公冶长第五》“子在陈”章和《孟子·尽心下》“孔子在陈”章均指出孔子在陈国时仍有相当多的一群弟子留在鲁国。很可能在孔子整个在外周游期间,或者其中的一段时间,子贡和冉求均在鲁国仕于季氏。《左传·定公十五年、《左传·哀公七年》和《左传·哀公十一年》提到子贡从政于鲁,也没有任何中断的证据,冉求在哀公十一年(前484年)首次提到,但那时他已是季氏宰和一支部队的指挥官,要达到此位一定会花不少时日。确实,《论语·子路十三》有“子适卫,冉有仆(孔子到卫国时,冉求为他驾车)”的记载,但我们不知道此次出行是何时。如果这正是孔子出发周游时发生的事,冉求可能仍在殷勤奉师,并在后来回到鲁国。
[98] ——译按:上注“子适卫”的记载,正是孔子最后一次周游的开始之时。此之前,孔子也曾出游,但那时冉求尚在年少,不及驾车。据本书注 之“译按”,子贡也曾随孔子周游。所以,至少在最初的随行周游者的行列中,应该有冉求和子贡。在孔子周游晚期,颜回病逝,冉求回鲁国做季氏宰,子路仕于卫国。冉求做季氏宰只是季康子的决定,不需要时间一步一步地达到这个位置。如果按照顾氏的逻辑,到了孔子周游列国末期,年近70岁的孔子应该是只身一人在外了。以情理论之,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99] 《孟子·万章上》:“孟子曰:‘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曰:“有命。”’”
[100] 《孟子·万章下》:“孔子有公养之仕。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101] 《论语·子路十三》:“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这一章被认为是孔子就要主持卫国之政了,但是,这一段明显是虚构的。见本书第十三章注[46]。
——译按:顾氏此论,大抵是受英文原典误译的影响。很少有人据此章认为孔子就要主持卫国之政了。子路之问,显然是假设,意在请求孔子评说卫国之政(子路后来在卫从政)。而孔子的答语,也不像是行将主政者的谋划。
[102] 《左传·定公十四年》。
[103] 《论语·卫灵公十五》:“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说的是,孔子离开卫国是因为他被问到了军事谋略,这是难以置信的。见崔,卷三;钱穆,第38—40页。
——译按:孔子因为卫灵公“问陈”而离开卫国,显然只是说,这场对话是孔子离开卫国的导火索。卫灵公的表现基本上不符合孔子的政治要求,在当时离开卫国是迟早的事情,只不过是孔子借用了这场令人沮丧的对话而已。
[104] 《左传·哀公三年》。
[105] 《论语·卫灵公十五》“子在陈”章和《孟子·万章上》:“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
[106] 《论语·述而第七》:“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107] 详见《左传·哀公三年》、《左传·哀公十一年》、《左传·哀公十四年》等。
[108] 这可能与《论语·颜渊十二》记载的子夏与司马牛的讲话有些不同,《弟子传》说子夏小孔子44岁,如若然,孔子周游列国开始时他至多才14岁。可是,可能司马牛在孔子周游前已就学孔子,而与子夏的交谈发生在后来。
[109] 详见《左传·哀公十四年》。
[110] 《论语·颜渊十二》“司马牛忧曰”章。
[111] 详见《左传·哀公十四年》。
[112] 《论语·颜渊十二》:“子夏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113] 《论语·颜渊十二》:“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114] 《孟子·万章上》:“孔子……微服而过宋。”
[115] 《论语·子罕第九》:“子畏于匡。”《论语·先进十一》:“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汝)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译按:没有理由认为“畏匡”与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是一回事。孔子一路多遇险情,《论语》只是择要而记。
[116] 《论语·卫灵公十五》:“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
[117] 《孟子·万章上》:“孔子为陈侯周臣。”陈侯是国君,而且一定是湣公,西元前501—前479年在位。见《孟子注疏》卷九、卷十和阎若璩《校正四书释地》卷四。
[118] 详见《左传·哀公二年》。
[119] 《论语·述而第七》:“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
——译按:从此章看,随行弟子还有巫马期。
[120] 《孟子·尽心下》:“孟子曰:‘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
[121] 《论语·公冶长第五》:“子在陈,曰:‘归与(欤)!归与(欤)!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子·尽心下》文微异。
——译按:其实,从《孟子》的记载中,人们才意识到“吾党小子”指的是留在鲁国的弟子。
[122] 孔安国《注》云,是叶公“僭取”了“公”号,可能正因如此,他有时被称作投机分子(僭臣)。邢昺解释说,楚国的统治者僭取了“王”号,而“他的所有的地方长官”都自称“公”(《论语》卷七)。这当然是周制沙文主义,因为没有正当根据说楚国曾臣服于周王室。更详尽的看法,见戴,卷七。
[123] 见原书第203—204页。
[124] 详见《左传》定公、哀公年间记事。
[125] 我们知道,孔子访问过蔡国(《论语·先进十一》:“从我于陈、蔡。”《孟子·尽心下》:“君子厄于陈、蔡之间。”),可能二人即在那里见的面,正如崔述所言(崔,卷三)。崔氏又言,孔子根本不可能(如后来传说所言)去访问楚国,除非说那时的蔡国已经是楚国的一部分了。早期资料都没说他去过楚国,《墨子》讲过孔子在楚国活动的荒唐故事(《墨子》(2),第206页),但这部分显然是后来加的,并且是杜撰出来的。见本书注 ,以及《墨子》(2),注 。
[126] 《论语·子路十三》:“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127] 《论语·子路十三》:“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128] 《论语·述而第七》:“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129] 《左传·定公十三年》。
[130] 此事的背景和日期有很大的争议,我遵从刘恭冕的解释,认为佛肸是晋国范中行氏的下属,而不是邢昺所说的赵简子的部下。见刘宝楠(卷二十)及《论语·阳货十七》。刘氏认为此事发生在西元前490年。
[131] 《论语·阳货十七》:“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132] 崔述坚决否定有过此事,他关切的主要是孔子的荣誉。不过,他的观点是乏力的(崔,卷二,以及注 )。冯友兰相信此事发生过,见冯(3),第37—38页。《墨子》提到过此事,但却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形式,并出现在可疑的《非儒篇》,见《墨子》(2),第211页。
[133] 崔述确实是最了不起的学者之一,因为他的正直,我也最尊敬他。但是,甚至是他也被不相信《论语·阳货十七》“佛肸召”章的过分渴求所出卖了。他宣称,在孔子时代,“夫子”这个词从未被用作当面称呼一个人,而《论语》的这一章正好这么做了(崔,卷二)。可是,事实上这种称呼亦出现在《论语·先进十一》“侍坐”章、《论语·颜渊十二》“棘子成”章、《论语·宪问十四》“君子道者三”章以及《论语·阳货十七》“子之武城”章。崔氏注意到了“侍坐”章和“子之武城”章,说它们可能是伪造的,但他显然忽视了另外两章。
——译按:这两章记载的事件,与孔子是否曾在鲁国做官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也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前一个事件发生在孔子在鲁国从政之前,后一个事件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期间,这两个时期都是孔子政治生涯的低潮时期。《论语》记载这样的事件,只能证明孔子从政的迫切心情,而并不是说孔子只能遇到这样的不合法的从政机会。
[134] 《左传·定公十四年》。
[135] 《左传·哀公二年》。
[136] 《左传·哀公十一年》。
[137] 《孟子·万章下》:“孔子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但卫国历史上没有“孝公”,这一定是指卫出公,见崔,卷三。
[138] 《史记·孔子世家》。
[139] 《论语·述而第七》:“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140] 《论语·公冶长第五》:“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141] 《左传·哀公十一年》引述的孔子在此关键点上说的话是:“鸟儿选择树木,树木怎么能选择鸟儿呢(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这是暗中设定了这位周游列国的哲学家是一只移栖的鸟儿,这也是一种自傲的表现。这个声明不像是孔子所说,而是反映了后来的情状。比如,孟子就完全是这种性格。
——译按:顾氏的这种判断未免过分拘谨。在外流浪了十几年的老人,发出这样的慨叹应该是在情理之中的。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因为孔子也有平常人的情愫,才更值得人们尊敬。
[142] 《左传·哀公十一年》。
[143] 《左传·哀公七年》。
[144] 《左传·哀公七年》。
[145] 《左传·哀公十一年》:“鲁人以币召之,乃归。”
[146] 《左传·哀公十一年》和《国语》(卷五)都说孔子拒绝正面答复,而只是私下让冉求知道他的看法。但从《论语》中孔子的率直表现来看,这是难以置信的。《论语》中孔子对季康子的言语是尖锐而坦率的。孔子也指责冉求,认为此事有他的责任。
——译按:不必因为孔子的这种态度而否认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因为孔子的这种态度并不难理解。此时的孔子已是近古稀之年,意识到实际的从政已然无望,影响实际政治运作的力量也非常有限。在这种背景下,选择不与当政者正面交锋完全是有可能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147] 《论语·先进十一》:“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148] 《论语·先进十一》:“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译按:《孟子·离娄上》:“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149] 孔子所谓“鸣鼓而攻之”,只是发泄愤怒的情绪而已,并不是对冉求的实际驱逐。这种宣泄在《论语》中多见,更不用说增税事件本身也不可能是冉求所能左右的。
[150] 《论语·子罕第九》:“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151] 《论语·述而第七》“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章通常被看作是孔子在卫国的事情,见崔,卷三。这就意味着冉求和子贡同时与孔子在卫国,而事实上他们两人此时可能正在鲁国。崔述认识到了这是个棘手问题,但试图以相当武断的方式加以解决。整个事件更像是发生在西元前479年的鲁国。此时,卫出公逃到鲁国避难(《左传·哀公十六年》),而作为应该负责的官员,冉求和子贡十分关注如何处理被流放者的问题,这对鲁国的政治命运是很要紧的。
[152] 《左传·哀公十二年》。
[153] 《左传·哀公十四年》。
[154] 我综合了《左传·哀公十四年》和《论语·宪问十四》的有关记载。《左传》与《论语》的不同之处,是说孔子拒绝将此事通告季孙,但他不会那么天真地希望无权的鲁公会采取独立的行动。《左传·哀公十四年》: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斋),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论语·宪问十四》:陈成子弒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弒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
[155] 《论语·先进十一》:“鲤也死,有棺而无椁。”
[156] 《论语·先进十一》:“颜渊死。”
[157] 详见《左传·哀公十四年》。
[158] 详见《左传·哀公十五年》以及《论语·子路十一》“闵子侍侧”章。
[159] 《论语·宪问十四》:“莫我知也夫!”
[160] 《论语·子张十九》:“叔孙武叔毁仲尼。”
[161] 《孟子·尽心下》:“孟子曰:‘《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
[162] 《礼记》卷一和《孔子世家》有这方面的记载,但与孔子的性格完全不符,正如崔述所认为的。见崔,卷四。
[163] 《论语·子罕第九》:“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164] 《论语·述而第七》:“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
——译按:孔子的意思是说,他自己的行为是对神灵的最好祈祷。
[165]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返),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
[166] 见本书注 。
[167] 《论语·子路十九》:“子贡曰:‘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
[168] 《孟子·公孙丑上》:“有若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169] 因为“附录”中解释的种种原因,对于《论语·乡党篇》中的内容,我在本章只使用了不多的一些章节。见原书第293页。
[170] 《论语·述而第七》:“子之燕(闲)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又:“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171] 《论语·学而第一》:“君子不重则不威。”《论语·先进十一》:“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172] 《论语·述而第七》“互乡难与言”章和《论语·子罕第九》“吾有知乎哉”章。
[173] 《论语·公冶长第五》:“匿怨而友于人……丘亦耻之。”
[174] 《论语·宪问十四》“南宫适问于孔子”章。
[175] 《论语·先进十一》“颜渊死”章、《论语·季氏十六》“陈亢问于伯鱼”章以及《论语·阳货十七》“子谓伯鱼”章。
[176] 《孟子·公孙丑上》:“孔子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
[177] 《论语·雍也第六》“祝 之佞”章和《论语·颜渊十二》“子张问达”章,《论语·宪问十四》:“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学而第一》:“巧言令色,鲜矣仁。”
[178] 《论语·学而第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里仁第四》“士志于道”章。《论语·述而第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泰伯第八》“三年学”章。《论语·宪问十四》:“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卫灵公十五》:“君子谋道不谋食。”
[179] 《论语·述而第七》:“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180] 《论语·季氏十六》“见善如不及”章明显称赞那种“用隐居来寻求实现他们的目标(隐居以求其志)”的人们,这很可能是插入《论语》中的道家思想。《论语·季氏十六》的大部分章节都是可疑的。无论如何,根据孔子的隐居观,如《论语·述而第七》“舍之则藏”和《论语·卫灵公十五》“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等例,并不能说明隐居本身是善的举动,而是当罪恶不可抗拒时,隐居会成为一个自尊之人的唯一作为。但是,这样的隐居者总是等待着采取行动和有效地参与政治的机会。
——译按:政治上的失意,在孔子晚年已成定局,加之他经常遇到的一些隐居者的影响,孔子很可能有时会有一些悲观隐退的想法。《论语》如实记载了孔子这方面的言论,并不一定是道家思想的插入。
[181] 《论语·学而第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论语·述而第七》:“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泰伯第八》:“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182] 《论语·述而第七》:“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阳货十七》:“孔子取瑟而歌。”
[183] 见《墨子·非乐篇》等。
[184] 《老子》第7、19、37、80章。可是,应该指出,《庄子·天下篇》把墨家有关这方面的思想谴责为“为之大过,已之不顺”和“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
[185] 见《韩非子·难势》和《商君书·垦令》等。
[186] 《论语·子路十三》:“近者悦,远者来。”
[187] 《论语·述而第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亦见《论语·阳货十七》“子之武城”章。
[188] 《礼记·杂记下》“子贡观于蜡”章。
[189] 《论语·子罕第九》:“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190] 《论语·述而第七》:“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191] 《论语·八佾第三》:“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译按:孔子此处所说的“不知”,明显是故意说反话。)《论语·子罕第九》:“吾有知乎哉?无知也。”
[192] 《论语·学而第一》“子禽问于子贡”章。《论语·八佾第三》:“子入大庙,每事问。”《论语·公冶长第五》:“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193] 《论语·雍也第六》首章、《论语·阳货十七》“子之武城”章、“宰我问三年之丧”章。
[194] 《论语·公冶长第五》末章,《论语·述而第七》第二章、“文莫吾犹人”章和“若圣与仁”章,《论语·子罕第九》“大宰问于子贡”章,《论语·宪问十四》“君子道者三”章。
[195] 《论语·宪问十四》:“莫我知也夫。”《论语·卫灵公十五》:“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也。”
[196] 《论语·卫灵公十五》“师冕见”章。
[197] 《论语·乡党第十》:“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198] 《论语·述而第七》:“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译按:在孔子看来,钓鱼的目不在于钓到多少鱼,射猎的目的也不在于射杀多少飞禽,而在于活动本身。这种活动既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在活动中表现人的礼仪和修养。所以,用网大量捕鱼,射杀正在孵化的鸟雀,都是为鱼而钓、为禽而射的,有害于君子的修养。
[199] 《论语·子罕第九》:“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200] 《论语·子罕第九》:“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译按:达巷党人的说法有两种相反的解释:讥讽或赞誉;孔子的答语亦然:严肃或玩笑。这四种意见的组合,确实不易定论。
[201] 《论语集释》,第493—494页。
──译注:朱熹《论语集注》:“闻人誉己,承之以谦也。”
[202] 《论语集释》,第1032页。《论语·阳货十七》:“前言戏之耳。”崔(2),卷二。
[203] 《论语·阳货十七》:“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204] 《论语·先进十一》:“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又:“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205] 《论语·宪问十四》:“原壤夷俟。子……以杖叩其胫。”
[206] 《孟子·公孙丑上》:“七十子之服孔子。”亦见钱穆,第56—62页。
——译按:习惯上所谓的孔子弟子“三千”,应该并不是一个确数,而是形容人数之众。而所谓“三千弟子”,也不必一定如颜回、子贡他们一样长期在孔门求学。在有关孔子弟子的此类问题上,过度拘谨的研究态度同样难以见到“真孔子”。
[207] 《论语·宪问十四》:“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
[208] 钱穆,第75—76页。
[209] 崔(2),卷三。
[210] 《论语·颜渊十二》:“子路无宿诺。”
[211] 《孟子·公孙丑上》:“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
[212] 《论语·公冶长第五》:“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论语·先进十一》:“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213] 《论语·述而第七》:“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凭)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214] 《论语·公冶长第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欤)?’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215] 《论语·先进十一》:“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室也。’”
[216] 《论语·宪问十四》:“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译注:“劳”的本义是关心、操心和担忧,即操劳。
[217] 《左传·哀公十四年》:“鲁有事于小邾,不敢问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弗能。”
[218] 《左传·哀公十五年》:“食焉,不辟(避)其难。”
[219] 《论语·先进十一》:“求也退,故进之。”
[220] 《论语·雍也第六》:“冉求曰:‘非不说(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汝)画。’”
[221] 《论语·公冶长第五》:“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论语·雍也第六》:“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222] 详见《左传·哀公二十三年》。
[223] 《论语·先进十一》:“言语:宰我、子贡。”及:“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臆)同屡中。”《孟子·公孙丑上》:“宰我、子贡善说辞。”《左传·哀公二十六年》。
[224] 《孟子·滕文公上》:“门人……入揖子贡。”
[225] 《论语·子张十九》“叔孙武叔语大夫”章和“陈子禽谓子贡”章。
[226] 《孟子·公孙丑上》:“子贡曰:‘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227] 《论语·雍也第六》:“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
[228] 《论语·公冶长第五》:孔子认为子贡是“瑚琏”之(祭)器;又:“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人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论语·宪问十四》:“子贡方(谤)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229] 《论语·先进十一》:“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230] 《论语·公冶长第五》:“子谓贡曰:‘女(汝)与回也孰愈?’子贡:‘赐也何敢望回?’”
[231] 《论语·里仁第四》:“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译按:孔子之意,是说根据一个人所犯过错误的类型可以判断其是否仁人,但并不能反过来讲不犯错误的人就没有资格做仁人。不过,颜回的品质,确实让西方人难以理解。
[232] 《论语·公冶长第五》:“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而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关于“轻裘”,见刘宝楠,卷六。
[233] 《论语·为政第二》:“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234] 《论语·先进十一》:“德行:颜渊……”《孟子·公孙丑上》:“颜渊善言德行。”
[235] 《论语·雍也第六》“颜回好学”章和“回也三月不违仁”章。《论语·子罕第九》:“语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及:“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236] 不仅没有颜回做官的证据,而且他的穷困一直延续到他去世时,这也就说明他一直没有从政。《论语·雍也第六》:“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先进十一》:“颜回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及:“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孟子·离娄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
[237] 崔述彻底驳斥了《韩诗外传》中颜回随侍鲁哀公并与之交谈的故事。见崔,卷一。
[238] 《论语·述而第七》: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239] 《论语·雍也第六》:“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此语亦见《孟子·离娄下》。
[240] 《论语·先进十一》“颜渊死”章。
[241] 《论语·先进十一》“颜渊死”章。
[242] 《论语·雍也第六》“宰我问仁”章及《论语·阳货十七》“宰我问三年之丧”章。
[243] 《论语·先进十一》:“言语:宰我、子贡。”《孟子·公孙丑上》:“宰我、子贡善说辞。”
[244] 《论语·八佾第三》“哀公问社于宰我”章及《公冶长第五》“宰予昼寝”章:“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钱穆相信,这些指责与《孟子·公孙丑上》所引述的宰我的观点中所体现的特点是不一致的。他认为它们是被误写进《论语》的,理由是,它们有一定程度的晦涩难懂以及内容并不完全可信。见钱穆,第50—53页。
[245] 《论语·八佾第三》“哀公问社于宰我”章。
[246] 《韩非子·显学》说,孔子死后,儒家有八派。这八派来自八位教师,其中三位是孔子直传弟子,即子张、颜氏(大抵是颜回)和漆雕开。子夏的被排除和颜回、漆雕开的被纳入同样令人惊讶。颜回年轻时去世,并死在孔子之前,他不可能建立起一个不同的学派。漆雕开在《论语》中只被提到过一次(《论语·公冶长第五》“子使漆雕开仕”章),而在其他著作中的记载也很少见。《墨子·非儒篇》提到了他,但只是因为他有“凶恶的外貌(形残)”而被用来谴责孔子。《史记·儒林列传》:“孔子死后,七十位弟子分散开来,并在诸侯之中周游(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
——译按:关于孔子弟子的分化和分派以及每一派的特点,请参阅拙著《孔子·孔子弟子》(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第二部分。
[247] 崔(2),卷一。
[248] 《孟子·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章。
[249] 《论语·先进十一》:“文学:子游、子夏。”
——译按:“文学”二字,在孔子时代泛指文物典章。
[250] 崔述怀疑《论语·阳货十七》“子之武城”章的可靠性,但说服力嫌弱。见崔(2),卷二。
[251] 《论语·先进十一》:“师(子张)也过,商(子夏)也不及。”
[252] 《论语·为政第二》:“子张学干禄。”《论语·颜渊十二》:“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
[253] 《论语·子张十九》首章和第二章。
[254] 《论语·子张十九》:“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255] 详见《史记》的《仲尼弟子列传》和《魏世家》。
[256] 孟子把子夏和曾子与某些无畏的刺客作了比较(《孟子·公孙丑上》),可是细心考查这段话的含义后,可知孟子认为他们具备的是道德之勇而非身体之勇。
[257] 《论语·子张十九》:“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258] 《韩非子·显学》:“(八儒)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孔(子)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
[259] 《论语·子张十九》:“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260] 《论语·子路十三》:“子夏为莒父宰。”
[261] 《论语·子张十九》:“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262] 《论语·雍也第六》:“子谓子夏曰:‘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263] 参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译按:最新研究表明,子夏正是战国时代三晋法家思想的创始人。详见拙著《卜子夏与三晋儒学》,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264] 更确切的称呼是曾参(cān),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但本书遵从更普遍的读法,称其为曾参(shēn)。
[265] 《孟子·离娄下》:“从先生者七十人。”
[266] 详见《孟子·离娄下》。
——译按: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曾子的行为确实与怯懦无关。曾子信奉传统的行为准则,即当某人客居一国时,对于该国的政治事务多半不具体参与,以避免嫌疑。如果他不在该国担任官职,更没有责任过问该国之事。但是,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曾子究竟不如孔子练达。
[267] 《论语·泰伯第八》:“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悖)矣。’”
[268] 《论语·泰伯第八》:“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又:“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269] 《孝经》的原作者被经常地但却错误地归之于曾子。见顾立雅(5),卷一,第35页。
[270] 《论语·学而第一》“曾子曰”章、《论语·子张十九》“曾子曰吾闻诸夫子”章,以及《孟子·离娄上》“曾子养曾皙”章。
[271] 这种怀疑由一位有才能的法国汉学家在一个世纪前作了表述,见毕瓯,第10—72页。
[272] 《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273] 见郭,第166—176页。理雅格翻译的《竹书纪年》中的一章说,一所帝国学校建于周朝初年,但事实上这就是青铜铭文上所谓的“习箭厅”之类的场所。某些后来的著作认为那里也教其他艺术,但对此并没有早期的证据。见上述引文;《书》“序”,第140页以及《诗》第458页注。
[274] 《论语·为政第二》:“君子不器。”
[275] 《论语·宪问十四》“子路问成人”章:“知、不欲、勇、艺、文之以礼乐。”
[276] 《论语·子路十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277] 《礼记·月令》:“季夏之月,天子衣朱衣。季夏行秋令,则秋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灾。”
[278] 马伯乐认为这是孔子的思想,并说是孔子得之于《尚书·洪范》,见马伯乐,第463页注[2]。但是,《尚书·洪范》包含了通常引证的所谓“五行”的说法,并穿插着神秘数字的使用。无论是这些,还是整篇文字的编撰,都没有与孔子思想同样早的特征(见本书注 ),说明它们确实是晚出的。阿瑟·韦利也把一种魔法思想归之于孔子,但他却认识到,上述那种宇宙论的魔法(天人感应论)“不属于《论语》中的孔子学说”,见韦利,第18页和第64—66页。
[279] 见顾立雅:《中国特色:中国世界观进化之研究》(芝加哥,1929年),第65页。这本书的主要前提是,汉代的形而上学体系有其相当早的根源,当然,这种看法完全是错误的。不过,尽管这本书写于20年前,但其中的一些不太重要的主张到现在我还是同意的。
[280] 一些早期文献,如《诗》、《书》之中,就有非常清楚的例子说明了榜样的作用。见《诗》和《诗》(2)书中各处,以及《书》的第498页。当然,《论语》的许多章节可以被解释为是在言说魔法般的影响,如《论语·为政第二》“为政以德”章、《论语·子路十三》“其身正,不令而行”章以及《论语·卫灵公十五》“无为而治”章。但是,它们也可以被解释为依靠榜样之力;而当我们全盘审察孔子的思想以及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时,便更可能是这样的了。详见《论语·里仁第四》首章、《论语·公冶长第五》“子谓子贱”章和《论语·卫灵公十五》“子贡问为仁”章。
[281] 详见《诗》,第260—261页;《诗》(2),第123页。
——译注:如《诗经》中的《采薇》:“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节南山》:“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无小人殆。”《大东》:“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角弓》:“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
[282] 这个表述是以对《书》、《诗》和《易》的仔细考察为基础的。在一些章节中,“君子”这个词的意思据上下文不太好确定。例如,有个意思可能接近于孔子对此词的用法,那就是《书·秦誓》“俾君子易辞”中“君子”的用法,这个词表面上看去可以认为不太早于孔子时期。很可能这个意思也出现在《易经》(第106页、第130页的《剥》和《大壮》)之中。
[283] ——译按:这种例外是意义深远的,有可能是表现了孔子思想的变化和发展。
[284] 《论语·述而第七》:“自行束修以上者,吾未尝无诲焉。”
[285] 《孟子·尽心下》:“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286] 《论语·述而第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287] 《论语·里仁第四》:“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288] 《论语·泰伯第八》:“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译按:此处的“谷”,大抵是指官俸,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物质报酬。
[289] 关于这一点,还没有可以定论的证据。可是,稍后时代,譬如墨子和孟子之时就是这样的了,这可能都与当时的经济条件有关。见《墨子》(2),第252页;《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致为臣而归”章。
——译按:《论语·子路十三》:“冉子退朝,子曰:‘何晏(晚)也。’”分明是冉求与孔子住在一处。这是孔子晚年的情形,因为冉求有权有势,生活条件有保障,孔子与冉求生活在一起,并把教学之所安排在冉求住处也是有可能的。另外,考虑到工作之便,冉求不太可能住在孔子的居处。但是,在孔子周游列国之前,无论条件如何,学生们还是更有可能集中生活和学习在孔子的居处。
[290] 《论语·子张十九》“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章特别指出了这一点。
[291] 《论语·为政第二》“视其所以”章、《里仁第四》“人之过也”章和《论语·公冶长第五》“宰予昼寝”章。
[292] 《论语·先进十一》“(子路等)侍坐”章和《论语·公冶长第五》“颜渊、季路侍”章。
[293] 《论语·先进十一》:“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294] 《论语·学而第一》“子贡曰贫而无谄”章和《论语·为政第二》“道之以政”章。
[295] 《墨子》(2),第252页。
——译按:《墨子·公孟》:“始吾游于子之门,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祭祀鬼神。”
[296] 《论语·子罕第九》“后生可畏”章。
[297] 《论语·述而第七》:“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
[298] 《论语·里仁第四》“富与贵”章和《公冶长第五》“孟武伯问”章。
[299] 《墨子》(2),229页。
——译按:《墨子·非儒》:“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攗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
[300] ——译按:《荀子·修身》:“不是师法而自用者,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妄乱无为也。”
[301] 《论语·雍也第六》首章和《论语·阳货十七》“子之武城”章。
[302] 《论语·阳货十七》“宰我问三年之丧”章。
[303] 《论语·述而第七》“不愤不启”章、《论语·泰伯第八》“学如不及”章、《论语·子罕第九》“颜渊喟然叹”章和《论语·宪问十四》“爱之能勿劳乎”章。
[304] 《论语·子罕第九》“譬如为山”章。
[305] 《论语·先进十一》“由之瑟”章。
[306] 《论语·宪问十四》:“子贡方(谤)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307] 《孟子·公孙丑上》。
——译按:《孟子·公孙丑上》:“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顾氏显然是凭印象综合了这些说法。
[308] 《论语·子罕第九》“达巷党人”章。
[309] 例见吴,十五卷和罗(2),四十二卷。
[310] 布赖斯,第23页。
[311] 罗(2),6.11b-12a。
[312] 《仪礼》,卷一,第229页。
[313] 郭(2),109b-110a。又详见《诗》,第440页;《诗》(2),第249页和《左传》。
[314] 《仪礼》,卷一,第200—201页、第244页。
[315] 《仪礼》,卷一,第18页。
[316] 汉字“礼”没有出现在《周易》里,容庚在他的《金文编》里所分析的许多青铜铭文中亦未列出这个字。在《尚书》(此书可能是儒家之前的)中,它以广义的形式出现在《金滕》篇中,但此篇的写作日期却有一些问题(《书》,第360页)。在《诗经》里有两次广义的出现(《诗》,第85、323页)。
——译按:在甲骨文中,“礼”是一种祭祀之名,当与音乐有关。从字形上讲,“礼”字既不从“示”,也不从“豆”,所谓祭器和祭品之义乃是后来的引申。见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5月),第2785—2788页。
[317] 阿瑟·韦利只在有限的意义上这样认为,他写道:“我认为孔子没有把这种魔力赋予任何典礼,除了那些由接受了天命的统治者主持的以外。”(韦利,第66页)。但是,整体魔力效应(“天人感应”)的观念与孔子总的思想模式是不相干的,正如我们在《论语》中所看到的。确实,《论语·颜渊十二》首章“颜渊问仁”有时被解释为:如果一个人(假定是国君)只用一天的时间实践“礼”,整个世界就会变成“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如果此章之意果真如此,实际上讲的就是魔力。但如果说此章难有此意,比较《论语·子路十三》“善人为邦百年”和“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说的却是一个良好的国君,在一定情形下需要一百年,而在另一种情形下需要一代人去纠正世间的弊病。
——译按:孔子讲“一日”不是说一整天,而是“一旦从某天开始”的意思,这与任何意义上的“魔力”无关。
[318] 《左传·宣公九年》。
[319] 《论语·颜渊十二》:“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320] 《论语·八佾第三》:“人而不仁,如礼何?”
[321] 《论语·八佾第三》:“为礼不敬……吾何以观之哉?”
[322] 《论语·八佾第三》:“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323] 《论语·阳货十七》:“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324] 《礼记·礼器》:“至敬无文……大圭不琢。”
[325] 见本书注 。
[326] 《礼记·礼运》:“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
[327] 《论语·子罕第九》:“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吾从下。”
[328] 《论语·宪问十四》:“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亦见《孟子·公孙丑下》。
[329] 这是相对来讲的。从我们的角度看去,儒家关于三年之丧的规定当然是过分的。见《礼记》卷一,第131、176—178页。
[330] 《论语·泰伯第八》:“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331] 《论语·公冶长第五》:“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332] 贝尔纳斯,第138页。
[333] 《论语·卫灵公十五》:“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又见《论语·八佾第三》“子夏问”章。
[334] 《论语·雍也第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35] 《论语·泰伯第八》:“立于礼。”《论语·子路十三》:“文之以礼乐。”《论语·季氏十六》:“不学礼,无以立。”
[336] 《论语·子张十九》“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章。
[337] 《论语·雍也第六》:“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叛)矣夫!”又见《论语·子罕第九》:“博我以文,约我以礼。”
[338] 《论语·卫灵公十五》:“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尽管《论语·卫灵公十五》的首章是大可怀疑的(见崔,卷三),但这里所引述的观点亦表述在《论语·里仁第四》“不仁者不可能久处约”和《论语·泰伯第八》“好勇疾贫,乱也”之中。
[339] 林,第107页。
[340] 兰,第13页。
[341] 亚里士多德,第1340页。
[342] 柏拉图(3),第401页;亦见柏拉图(4),第672页。
[343] 《论语·八佾第三》“子语鲁大师乐”章、“子谓《韶》”章,《论语·述而第七》“子在齐闻《韶》”章,《论语·泰伯第八》“师挚之始”章和《论语·阳货十七》“子曰礼云”章。
[344] 《论语·子罕第九》“吾自卫返鲁”章。
[345] 《论语·述而第七》“子与人歌”章和《论语·阳货十七》“孺悲欲见孔子”章。
[346] 柏拉图(3),第398—400、424页;亦见柏拉图9(4),第700—701页。《论语·卫灵公十五》:“子曰:‘放郑声。’”
[347] 《孟子·公孙丑上》:“闻其乐而知其德。”
[348] 《论语·先进十一》“子曰由之瑟”章和“侍坐”章之“(曾点)鼓瑟希”。
[349] 《论语·宪问十四》“子路问成人”章。
[350] 《论语·泰伯第八》:“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351] 阿特休勒,第79—80页。
[352] 阿特休勒,第77页。
[353] 见勒马斯特。
[354] 《论语·为政第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小车无 ,其何以行之哉?”我用简化修饰的方法将这一段的译文作了删节。
[355] 《论语·卫灵公十五》:“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356] 《论语·公冶长第五》“子张问孔文子”章、《论语·宪问十四》“公叔文子之臣”章和《论语·卫灵公十五》“子曰臧文仲”章。
[357] 《论语·公冶长第五》:“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358] 《论语·阳货十七》:“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逾之盗也与(欤)?”
[359] 《论语·子路十三》:“言必信,行必果,铿铿然小人哉!”
——译按:孔子之深意是,一个人当初的“言”和“行”,后来会逐渐暴露出是错误的,这样,自然就不必有“信”和“果”。
[360] 《论语·学而第一》:“过则勿惮改。”《论语·子张十九》“子贡曰君子之过”章。
[361] 《论语·雍也第六》:“仁者先难而后获。”《论语·颜渊十二》:“先事后得。”《论语·卫灵公十五》:“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362] 《论语·为政第二》:“见义不为,无勇也。”
[363] 《论语·宪问十四》:“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卫灵公十五》:“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364] 例如,这是在《易经》里使用的唯一的一种意思(《易经·大过》:“老妇得其士夫。”《归妹》:“士刲羊。”)。这种品格在历史上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但这将使我们离题太远,故不能在此详述。
[365] 赫恩肖,第437页。
[366] 《论语·宪问十四》:“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正文里的(英文)译文,根据的是阿瑟·韦利的翻译。
[367] 《论语·泰伯第八》:“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368] 《论语·子罕第九》:“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369] 《论语·子罕第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370] 《论语·卫灵公十五》:“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371] 《论语·里仁第四》:“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372] 《论语·颜渊十二》:“攻其恶,无攻人之恶。”
[373] 《论语·卫灵公十五》:“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374] 《论语·述而第七》:“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译按:此处所谓“三人”,泛指众多之人,不是必指三人。
[375] 《论语·里仁第四》:“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376] 《论语·雍也第六》:“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事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377] 《论语·宪问十四》:“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参看《十三经注疏》之“校勘记”。
[378] 《论语·为政第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379] 《论语·宪问十四》“为命”章。
[380] 《论语·卫灵公十五》:“辞,达而已矣。”参看《礼记》卷一,第233—234页。韦利还限定“辞”的意义为“请求,使命,为不能照料好某项工作而作的辩解,等等”(韦利,第201页注[2])。可是,对于它的“言语”的意义,可见《论语·泰伯第八》之“出辞气”章、《孟子·公孙丑上》之“子贡善为说辞”章,以及《书》第628页。
[381] 《论语·阳货十七》:“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382] 《论语·里仁第四》:“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383] 《论语·卫灵公十五》:“远佞人……佞人殆。”
[384] 《论语·雍也第六》:“不有祝 之佞,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385] 《论语·阳货十七》:“恶利口之覆邦家也。”
[386] 《论语·子路十三》:“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387] 《论语·宪问十四》:“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
[388] 《论语·学而第一》:“君子不重则不威。”
[389] 《论语·八佾第三》:“君子无所争。”《论语·卫灵公十五》:“君子矜而不争。”
[390] 《论语·为政第二》:“慎言,慎行,禄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十三》:“欲速,则不达。”
[391] 《论语·学而第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392] 《论语·里仁第四》:“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393] 《论语·颜渊十二》“子张问达”章,以及《论语·卫灵公十五》:“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394] 《论语·子路十三》:“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395] 《论语·卫灵公十五》:“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396] 《论语·泰伯第八》:“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子路十三》:“君子泰而不骄。”
[397] 《论语·子路十三》:“君子易事而难说(悦)也,说(悦)之不以道,不说(悦)也;及其使人,器之。”
[398] 《论语·为政第二》:“君子周而不比。”《论语·子路十三》:“君子和而不同。”
[399] 《论语·里仁第四》:“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述而第七》:“君子坦荡荡。”《论语·泰伯第八》:“曾子曰:‘临大节而不夺。’”
[400] 《论语·颜渊十二》:“君子不忧不惧。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宪问十四》:“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401] 《论语·公冶长第五》:“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斯焉取斯?’”《论语·里仁第四》“里仁为美”章、“德不孤”章和《论语·子罕第九》“子欲居九夷”章。
——译按:子贱并非寻常鲁国人,乃是孔子弟子宓子贱。
[402] 《论语·学而第一》:“君子……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卫灵公十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403] 《论语·学而第一》:“泛爱众而亲仁。”
[404] 《论语·学而第一》:“主忠信,勿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颜渊十二》:“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导)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
[405] 《论语·阳货十七》“公山弗扰以费畔”章、“佛肸召”章。
[406] 威廉姆逊,卷一,第61页。
[407] 《论语·学而第一》“弟子入则孝”章、“子夏曰”章。
[408] 《论语·子路十三》“诵诗三百”章。
[409] 《论语·述而第七》:“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译按:“文、行、忠、信”之“文”,应该是“文饰礼仪”之“文”,这样才能与其余三项处在同一逻辑层次上。
[410] 《论语·为政第二》和《论语·子路十三》都提到“《诗》三百”。
[411] ——译按:比如,《论语·八佾第三》中子夏提到了“巧笑倩兮”就是在现存《诗经》中所没有的诗句,即所谓“逸诗”。
[412] 《论语·阳货十七》:“子谓伯鱼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欤)?’”
[413] 《论语·阳货十七》:“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泰伯第八》:“子曰:‘兴于《诗》。’”
[414] 见韦利对此用法的讨论,《诗》(2),第335—337页。
[415] 《论语·季氏十六》:“不学诗,无以言。”见戴望《戴氏注论语》。
[416] 《论语·子路十三》:“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417] 见钱玄同;顾(4);《诗》(2),第335—337页。
[418] 《国风·齐风·鸡鸣》:“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
[419] 《论语·学而第一》“子贡曰”章和《论语·八佾第三》“子夏问曰”章。
[420] 顾(4),第347页。
[421] 《礼记》由戴圣在西汉时编成,他使用各个时期的材料,其中最早的材料远到何时是有争论的。的确,它们中的一些,由于它们的风格和内容,产生的时期远晚于孔子时代。《周礼》描绘了一个有秩序的集权政府的理想体制,这个政府被认为存在于西周初年,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事情,并且也被来自确实是早期的著作和金文的所有证据所驳倒。马伯乐认为它的日期起自西元前4世纪,在汉代编成并被掺入了其他内容(马伯乐,Ⅻ)。胡适认为,它是汉代的著作[胡(2),第222页]。
[422] 《伪书》,卷一,第269—280页。
[423] 详见《左传》各处对“礼”的言说。
[424] 当然,我在此仅指今文本的《尚书》,尽管其中也包含了一些伪篇;见顾立雅,第55—93页、第97页注[1][2]。《墨子》中的“尚书”一词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在墨子时代就有了这样一个集子。汉字“尚”字在几个青铜铭文中被用作“保存”之意(见容庚,2.2b-3a);因此,“尚书”的本义可能仅指档案。而且,孙诒让相当正确地指出,在《墨子》中,“尚书”二字本无意义,所以,在校订时就被他删去了。见《墨子》,8.15a。
[425] 《论语·为政第二》“或谓孔子”章、《述而第七》“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章和《论语·宪问十四》“子张曰”章。这里没有把《论语·先进十一》“子路使子羔为费宰”章(其中有“何必读书”句)包括在内,因为那是泛言书本。
——译按:《论语》把《诗》、《书》并列言之,似乎对顾氏的观点不利。事实上,更宽容一些的看法应该是,《书》在孔子时代就有,只不过与《诗》一样,不同于后世《尚书》的篇目而已;至于今、古文本之说,与孔子更无关系。
[426] 《论语·学而第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黄式三指出,“说”在此章的意义是“因完全理解而高兴”,这与此汉字的原音原义有关联(见黄,1.1b)。
[427] 《论语·学而第一》“子禽问于子贡”章和《八佾第三》“子入太庙”章。
[428] 《论语·为政第二》:“多闻阙疑,多见阙殆。”“殆”字在此之意是“只是有可能的东西”,这种解释比较适合原文的上下文。同样的用法出现在《书》(第548页)和《孟子·梁惠王上》“殆有甚焉”中。这个字通常的意义是“危险的东西”,见《为政第二》“学而不思”章和《卫灵公十五》“颜渊问为邦”章。
[429] 《论语·卫灵公十五》:“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430] 《论语·阳货十七》:“好知不好学,其弊也荡。”
[431] 《论语·为政第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432] 《论语·公冶长第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433] 《国语》,卷五、卷十三。
[434] 《论语·学而第一》“弟子入则孝”章、《阳货十七》“子之武城”章和《子张十九》“卫公孙朝问”章。
[435] 《墨子》(2),第233页。
——译按:《墨子·公孟》:“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
[436] 康,11.1a。
[437] 康,10.1b。这并非意味着孔子撰写了现在流传的所有古籍。康氏认为,它们中的一大部分是刘歆伪造的。
[438] 康,10.2b—3a。
[439] 《论语·述而第七》:“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440] 《史记·孔子世家》。现存《诗经》有305篇,另外还有6篇仅存篇名。
[441] 崔,卷三。
[442] 《论语·为政第二》“《诗》三百”章和《子路十三》“诵《诗》三百”章。
[443] 《论语·子罕第九》“唐棣之华”章。
[444] 指“郑声”,见《论语·卫灵公十五》“颜渊问为邦”章,以及《阳货十七》“恶郑声之乱雅乐”。
[445] 《论语·子罕第九》:“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译按:这是说诗篇与配乐的关系,因为每一首诗在原初都是有乐曲相配合的。所谓“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说《雅》、《颂》两部分的诗篇都与其原来的乐曲相配合了,并不是整理了诗篇的文字部分。
[446] 《孔子世家》;崔,卷三。
[447] 《孟子·尽心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译按:孟子此言,是说不能片面地理解《尚书》和其他古籍的历史记载,并不是对《尚书》本身的可靠性有所怀疑。
[448]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昭公二十五年》:“有 鹆来巢。”《僖公十六年》:“六鹢退飞过宋。”
[449] 这种正统观点,即孔子编著《春秋》的说法,为乔治·A.肯尼迪近来的研究所遵从。他绘制了一张地图,显示出与各国相关联的所有资料,并总结道:“对其他所有事情的记载分量都一样……只有孔子周游列国途经的各个国家,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记载。”(肯尼迪,第48页)可是,他收集的有价值的资料却承认了另外的解释。如果我们把他的地图和图表看成是其他国家与鲁国政治关系的说明,它们会更有意义。例如,他在第45页上的图表显示出,西元前584年之前,从不记载吴国国君的死亡,但此后就都有了。确切地说,正是在西元前584年,包括鲁国在内的北方国家才开始与吴国交往(《成公七年》)。
肯尼迪的主要论点——这部书没有某种深奥的原则(即所谓“春秋笔法”)——是可以成立的,而他亦为此整理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
[450] 《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451] 肯尼迪。
[452] 理雅格译《左传·绪论》,第5—6页。
[453] 《孟子·离娄下》提到了“鲁之《春秋》”,但接着又说这本书记载的是“齐桓公和晋文公的事务(其事则齐桓、晋文)”。可我们知道,这部书是鲁国的编年史,只是偶尔提到这些人物。同样的反对理由是,孟子又说这部书是对“天子之事”(《孟子·滕文公下》)的记叙。许多学者怀疑孟子讲的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见顾,第42页;以及《左传·绪论》,注[4]。
[454] 《孟子·滕文公下》:“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译按:孔子所说的“知”,并不是扬名,而是让别人理解他。
[455] 《孟子·万章上》:“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456] 《礼记·杂记下》:“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仪礼》之中就有这方面的篇章。
[457] 《论语·为政第二》“子张问十世可知”章和《八佾第三》“夏礼吾能言”章。
——译按:孔子说“十世可知”,并不是断言礼在未来的变化形式,而是从事理的角度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458]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编次其事,故《礼记》自孔氏。”
[459] 《论语·子罕第九》引述孔子的话说,他从卫国返回鲁国后,“乐得到了校正(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这可以是说他校正了某些著作,但也可以是说他只不过是教授了鲁国的宫廷乐师(见《八佾第三》“子语鲁大师”章和“师挚之始”章)。
[460] 显然是用于占卜的几枚骰子在两座新石器文化的“黑陶作坊”遗址中被发现。新石器文化早于商朝,见顾立雅,第176—177页。
[461] ——译按:《述而第七》:“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学《易》,不应被怀疑,只是学《易》与占卜和作《易》有着根本区别。
[462] 冯(2),第202页;马伯乐,第459页。
[463] 《论语·八佾第三》“三家者”章、《述而第七》“子谓颜渊”章和《子罕第九》“衣敝缊袍”章。
[464] 《论语·学而第一》“子贡曰”章、《为政第二》“《诗》三百”章、《八佾第三》“子夏问”章和《颜渊十二》“子张问”章。
[465] 《论语·为政第二》:“《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译按:此诗出自《诗经·鲁颂· 》。
[466] 韦利,《诗》(2),第275页。理雅格依照传统注释来翻译这首诗(《诗》,第611—613页),但是,特别是从这首诗第一节的末尾来看,把“思”译成“他想”就显出了它的荒谬。
[467] 《论语·为政第二》“或谓孔子”章和《宪问十四》“子张曰书云”章。
[468] 《论语·为政第二》:“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此章与载于《尚书·君陈篇》的文字稍有不同。它是在古文《尚书》之中,而古文《尚书》则被学术界一致认为是伪造的。伪造者把出现在《论语》中的这段引文收入,这并非不可能。所以,尽管我们不能十分有把握地确定其原意,但却能够很清楚地说明孔子曲解了它的原意,因为“有政”本是指一个有官位的人。孔子回避了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他面对弟子时深感窘迫,也就是说,孔子甚至没有得到过一个与弟子们官职相等的职位。
[469] 比较《仪礼》,卷一第119页和《论语·八佾第三》“射不主皮”章;卷一第147页和《述而第七》“子食于有丧者之侧”章;卷一第89页和《述而第七》“子于是日哭”章;卷一第153页和《乡党第十》“君子不以绀 饰”章;卷二第363页和《子路十三》“南人有言”章。
[470] 《论语·子路十三》“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比较《易经·恒卦》和《礼记·缁衣》“子曰南人有言”章。
[471] 《论语·子路十三》“樊迟请学稼”章。
[472] 《论语·子路十三》“诵《诗》三百”章。
[473] 威尔逊,第100—101页。
[474] 温德尔班德,第24页。
[475] 柏拉图(2),第65—66页;泰勒,第164—171页;A. K. 罗杰斯,第156—157页。
[476] 威尔逊,第100—113页。
[477] 《论语·子张十九》“子贡曰文武之道”章。
[478] 《孟子·尽心下》末章。
[479] 梅,第185页。
[480] 高本汉(2),第4页。
[481] 比较《论语·颜渊十二》“仲弓问仁”章和《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以及《子路十三》末章和《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482] 梅,第181—185页。
[483] 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另外,这本书还引述了郑国子产的预言,说陈国“不出十年”将被灭亡;九年零五个月后,这种结局果然出现了(《左传·襄公三十年》、《左传·昭公八年》)。在《左传》中,这样的预见是有案可查的。
[484] 罗,1.25.1,6.58.4;刘鄂,190.2。
[485] 顾立雅(3)。
[486] 《墨子·公孟》:“子墨子曰:‘儒者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
[487] 《论语·八佾第三》“夏礼吾能言”章、“子入太庙”章、“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章和《先进十一》末章。
[488] 《论语·宪问十四》“子张曰”章和《阳货十七》“宰我曰”章;《孟子·滕文公上》。行三年之丧的最初时期是什么时候,这是个引起很大争论的难题;如果我们可以根据《孟子·滕文公上》的述说下判断的话,在孔子时代,这种做法并不普遍。
[489] 《论语·述而第七》:“子不语怪力乱神。”
[490] 《论语·泰伯第八》:“禹,致孝乎鬼神。”
[491] 《论语·先进十一》:“子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492] 《论语·雍也第六》:“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
[493] 顾立雅(2),第82—90页。我在该文中的更一般性的结论需要作重大修改。
[494] 康德,卷九,第308页。
[495] 《论语·为政第二》“非其鬼而祭之”章、《八佾第三》“禘自既灌”章、“或问禘之说”章和“祭如在”章。
[496] 《论语·述而第七》“子疾病”章:“丘之祷久矣。”
[497] 正如上文所述,“天”和“帝”本来是不同的,但在孔子时代之前就已经合而为一了。
[498] 《论语·雍也第六》“子见南子”章、《述而第七》“天生德于予”章、《子罕第九》“子畏于匡”章、《先进十一》“颜渊死”章和《宪问十四》“莫我知也”章。
[499] 《尚书·顾命》:“王曰:‘今天降疾。’”
[500] 《论语·公冶长第五》:“子贡曰:‘夫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501] 《论语·卫灵公十五》:“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译按:此章的主旨是孔子关于社会分工的思想,似与对待成功和财富的态度无关。君子的社会责任是谋道,不是种田。
[502] 《诗》,第528—529页。
——译按:《诗经·云汉》:“靡神不举,靡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
[503] 郭沫若(2),202b—203b。
[504] ——译按:《墨子·公孟》:“鲁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于鬼神。”
[505] 顾立雅,第214—218页。
[506] 《诗》,第198—200页;《诗》(2),第268页;《左传·僖公三十年》等。
[507] 详见《墨子·明鬼下》。
[508] 详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509] 威尔伯,第153、193页。
[510] 《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以及《礼记》,卷一,第173页。中国学者相信使用人像(俑)在先,而用活人殉葬源于此,但实际的历史情况正好与这种意见相反。
[511] 《礼记·檀弓下》“陈子车死于卫”章。
[512] 《诗经·大雅·下武》:“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513] 郭沫若(2),133a。
[514] 《论语·雍也第六》“子谓仲弓”章。据说“子谓仲弓”应该被理解为“对仲弓说”,但《子罕第九》的“子谓颜渊”却说明,合适的理解应该是“评说颜渊”。
——译按:依《论语》体例,“谓……曰”是说“对……说”;而“谓……”则是“评说……”。
[515] 《论语·雍也第六》“雍也可使南面”章。
[516] 威尔逊,第106页;雅各布森,第213页;欧文,第338—341页。
[517] 韦伯,第293页。如果我们能够说韦伯对孔子和儒学的评论都是公平的洞察的话,那将是很令人高兴的,但不幸的是,这不是实情。不过,韦伯确实作了一些敏锐的观察,就他所能用到的译本和第二手材料而言,这已经是相当惊人的了。
[518] 《论语·八佾第三》:“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亦见《礼记》,卷二,第272、311页。
——译按:《礼记·礼运》:“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仲尼燕居》:“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上述孔子所说“之于天下”,只是说“对于天下人而言”,似乎并没有顾氏所说那么复杂的含义,即没有宗教或哲学含义。
[519] 被认为是孔子所说的只有两章,即《论语·为政第二》的“五十而知天命”和《季氏十六》的“畏天命”。极常见的形式是前一种说法,但它的绝对自满自足的口气,让人觉得靠不住。后者的说法也是可疑的,因为这一章使用了数字“三”,并且其所表现的思想具有独断性的倾向。
[520] 《墨子》(2),第202、234页。
——译按:详见《墨子·非命》。
[521] 《论语·雍也第六》“哀公问”章和《先进十一》“季康子问”章的“短命”。
[522] 《论语·宪问十四》“子路问成人”章之“见危授命”。
[523] 《论语·宪问》:“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524] 《论语·雍也第六》“冉求曰”章和《子罕第九》“譬如为山”章。
[525] 《论语·颜渊十二》:“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这是断章引文,但我相信并不是一种破坏原意的做法。
——译按:子夏所引述的说法事实上是当时流行的俗语,所以才出现在当时其他一些思想家的言论中。尽管这种说法与孔子的有关观点基本一致,但那确实不是孔子的说法。如果真是孔子所言,依照《论语》的体例,应该采用“闻诸夫子”之类的提法。
[526] 《论语·卫灵公十五》:“君子忧道不忧贫。”
[527] 此字未列入孙海波的《甲骨文编》中;而董作宾告诉我说,在他20多年的甲骨文研究中,从未遇到过这个汉字(1947年11月18日的口头交谈)。
[528] 容庚(2.23)列举了出现的4个“道”字的金文;郭沫若(2),59b,129a,186a,198b;亦见郭沫若(2),140b。
[529] “道”字的“道路”或“渠道”之意:《易》,第9页;《诗》,第52、55、151、155、156、160(三次)、196(两次)、197、206、218(两次)、247、261、331、332、336、349、353、418、424、441、546、617页。“行为”的意思:《书》,第99、102、113、119页。“说道”或“陈述”的意思:《书》,第338、558页;《诗》,第74页(两次)。“行动路线”的意思:《易》,第76、93、108页;《书》,第477、567页;《诗》,第469页。
——译按:“道”还应该有“导向”的意义,因为繁体字的“导(導)”与“道”在字形和语音方面都有联系,成为通假字。
[530] 《论语·子罕第九》“不忮不求”章和《卫灵公十五》“道不同”章。
[531] 《论语·先进十一》:“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532] 《论语·里仁第四》:“参(曾子)乎,吾道一以贯之。”《卫灵公十五》:“赐(子贡)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非也,予一以贯之。”
——译按:所谓“一以贯之”,明显是一种方法,而不是实在的内容。顾氏的解释略显牵强。
[533] 中文名字顾乐真,为本书作者顾立雅之夫人。
[534] 克里尔,洛兰,第22—25页。
[535] 《论语·雍也第六》:“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536] 《论语·里仁第四》:“朝闻道,夕死可矣。”
[537] 顾立雅(4),第127—131页。
[538] ——译按:见《尚书·康诰》。此文一般认为是周公对其弟康叔的训诫之辞。
[539] 《论语·里仁第四》:“事父母,几谏。”
[540] 《论语·子路十三》:“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541] 见《礼记》,卷一,第140页;《家语》,卷十。虽然是两处记载,但却是微有不同的一件事。《论语》没有提到过家族复仇,对这种做法的倡导似乎也不符合孔子的脾性。荀子则对此感到痛惜(《荀子》,第343页)。
——译按:见《礼记·檀弓》、《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荀子·议兵》。
[542] 《论语·学而第一》“弟子入则孝”章、《为政第二》“或谓孔子”章(参见《学而第一》“有子曰其为人”章)、《颜渊十二》“齐景公问政”章和《阳货十七》“子曰小子”章。
[543] 《诗》,第273、249页。
——译按:《诗经·南山有台》:“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泂酌》:“岂弟君子,民之父母。”
[544] 《论语·颜渊十二》:“子夏曰:‘商闻之矣: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译按:子夏引用的也是当时流行的俗语,并非孔子所言,尽管它与孔子思想并不矛盾。
[545] 《论语·子罕第九》“子欲居九夷”章、《子路十三》“樊迟问仁”章和《卫灵公十五》“子张问行”章。韦利,第108页。
[546] 赫梅尔,第352页。
[547] 《论语·子路十三》:“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548] 《论语·颜渊十二》:“哀公问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549] 《论语·里仁第四》“见贤思齐”章、《公冶长第五》“已矣乎”章、《颜渊十二》“司马牛问君子”章和《卫灵公十五》“躬自厚”章。
[550] 《论语·子路十三》“子适卫”章、“善人教民”章、“以不教民战”章和《阳货十七》“子之武城”章,参见《为政第二》“道之以政”章。
[551] 《论语·阳货十七》:“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552] 我并未忘记《论语·泰伯第八》中的一章:“夫子说:‘可以使人民去遵从,但却不能使他们去理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这一章的意思并不完全清楚,我们不知道它的语境和具体的参照系。
——译按:其实,在孔子时代,很难想象让大众参与政治,就连孔子本人也不易从政。即使是当代社会,普通人对国家的重大决策又能参与多少呢?大众的接受普通教育与实际参与政治并不能等同。
[553] 《论语·子路十三》:“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这不是仅仅指军训,参见此章之前的一章“善人教民七年”。
[554] 许多学者对所谓的“仁”的美德长篇大论。但我们在读罢他们的讨论并考虑了《论语》中有“仁”出现的章节之后,仍然难以看出如何才能给“仁”下一个比“德行”、“美德”或“完善之德”更接近的定义。汉字“德”也是“德行”之意,有时它毋宁是指一个人或事物的品质,不论是好的或坏的,因为我们可以讲一个囚犯的“罪(恶的德)行”。可是,在《论语》中,德与仁有时能互换,这在《宪问十四》“有德者”章中是特别明显的,并且当我们比较《雍也第六》“樊迟问知”章和《颜渊十二》“樊迟从游”章时,也会看出这一点。韦利几乎总是把“德”解释为“内在力量”。在我看来,“德”似乎是个在后来比在孔子时代更普遍使用的概念。然而,当它表达在《宪问十四》“或曰以德报怨”章时,似乎是“内在力量”的解释也站不住脚了。
[555] 《论语·宪问十四》中子路、子贡与孔子讨论管仲的章节,以及《卫灵公十五》:“君子贞而不谅。”
[556] 《论语·先进十一》“季子然问”章。
[557] ——译按: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与当代民主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御史的劝谏只是提出意见,君主能否接受,并无制度上的保证;而且,这种意见又往往是时效性的,针对一人一事而发,不可能具有长久的法律效力。顾氏之论未免浮泛,且过分乐观。
[558] 《论语·里仁第四》“苟志于仁”章、“放于利”章、“君子喻于义”章,《雍也第六》“樊迟问知”章,《述而第七》“富而可求”章和《宪问十四》“子路问成人”章。
[559] 《论语·宪问十四》“子路问成人”章和《子张十九》首章。
[560] 《论语·述而第七》:“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561] 《论语·里仁第四》:“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562] 《论语·宪问十四》:“知其不可而为之。”
[563] 《孟子·公孙丑上》:“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564] 《论语·颜渊十二》:“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565] 《论语·述而第七》:“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566] 《论语·子罕第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567] 《论语·卫灵公十五》:“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568] 《论语·子罕第九》:“毋友不如己者。”亦见《学而第一》“君子不重则不威”章。
[569] 康德,卷九,第339页。
[570] 《论语·学而第一》:“泛爱众而亲仁。”
[571] 《论语·里仁第四》“子曰参乎”章。
[572] 《论语·卫灵公十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73] 《论语·雍也第六》:“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574] 康德,卷八,第47页。
[575] 康德,卷九,第230页。
[576] 《论语·子罕第九》“子欲居九夷”章。
[577] 《论语·颜渊十二》“季康子问政”章。
[578] 《论语·子路十三》:“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
[579] 《论语·雍也第六》:“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580] 《论语·阳货十七》:“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581] 《论语·公冶长第五》“宰予昼寝”章。
[582] 《论语·阳货十七》:“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583] 确实,《论语·季氏十六》中的一章说:“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那些生来就拥有知识的人,是最高层次的人)但这部分几乎肯定是虚构的,见原书第221页。
[584] 《孟子·离娄上》“孟子曰规矩”章。
[585] 甚至孟子都认为《书》是“与其都相信它,还不如没有它”。(《孟子·尽心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而在荀子这位极权主义者那里,宣称学习的方法是“开始于诵读经典,结束于学习礼”。(《荀子·劝学》:“始于诵经,止于学礼。”)
——译按:上述孟子的说法并不是怀疑《书》的思想,而是在探讨《书》的记述方式。
[586] 《论语·阳货十七》“宰我问三年之丧”章。
[587] 《论语·子罕第九》:“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588] 《论语·宪问十四》“微生亩”章。
[589] 《孟子·万章下》首章。
[590] 《论语·里仁第四》:“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591] 这种解释尤其不适合《论语·雍也第六》的“务民之义”。
——译按:此“义”作“宜”解,后儒亦有所谓“义者宜也”的说法。
[592] 《论语·学而第一》:“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593] 《论语·宪问十四》:“见利思义。”
[594] 一个特别清晰的例证是《论语·子罕第九》“子曰麻冕”章。
[595] 《论语·卫灵公十五》:“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596] 《论语·为政第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597] 《论语·述而第七》:“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韦利把“古”解释为“过去”,这比常见的“古人、古事”的解释更确切一些。尽管孔子和孟子相隔仅一个世纪,后者还是把孔子列在“古圣”之中(《孟子·公孙丑上》“公孙丑问曰夫子加之齐之卿相”章)。
[598] 《论语·八佾第三》:“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正文的翻译所根据的是此章与出现在《礼记》(卷二,第324页)和《家语》(卷一)的不一致的说法的相互比较。《家语》未被引征为孔子言论的可靠资料,但可以被理解为对于孔子观点的相对早期的看法。“文献”二字未译出,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如何翻译它。
——译按:《礼记·中庸》:“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孔子家语·问礼》:“孔子言:‘我欲观夏,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乾坤》焉。’”至于“文献”的传统解释,认为是指典章文物和相关的贤能之人,“献”与“贤”通。
[599] 《论语·为政第二》:“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在正文中,“殆”的翻译可见本书注 。
[600] 《论语·卫灵公十五》:“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601] 《论语·述而第七》:“多闻,择其善者而存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从文意上讲,末句的意思是“这些是……的阶段(步骤)”。我所知道的所有注释家和翻译者都将此处的“次”理解为“下一个”或“第二的”,这样,我们就得将这句话解释为“这是第二好(次一等)的知识”,亦即相对于生来拥有的知识而言是次一等的。但是,难道孔子相信会有什么生来就能拥有的知识吗?这是很令人怀疑的。而且,这种说明对这一章来说是个无意义的附加物,显然出现得太突兀了。很可能是,“次”的原意是指暂住之地,即旅行中的一个中途点(旅次);《易》的原文(《易经·旅卦》“旅焚其次”)以及《里仁第四》中的“造次必于是”可能就是此意。在此,孔子讲的是求取知识或智慧的途中的一个阶段。
[602] 《论语·卫灵公十五》:“子曰:‘赐也,女(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欤)?’对曰:‘然,非与(欤)?’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603] 康德,卷九,第231页。
[604] 《论语·子路十三》“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章和《卫灵公十五》“众恶之”章。
[605] 比如,孔子有一种朴素的信仰,即有可能预料到礼的使用在未来一百年的变化;见《论语·为政第二》“殷因于夏礼”章。
[606] 雅各布森,第203页;参见原书177页。
[607] 《论语·学而第一》:“君子过则勿惮改。”《述而第七》:“不善不能改,是呈吾忧也。”和“三人行”章,《子罕第九》“法语之言”章,“主忠信”章,《卫灵公十五》:“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子张十九》:“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608] 《论语·为政第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609] 《孟子·离娄下》:“仲尼不为已甚者。”
[610] 《论语·子路十三》:“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参见《孟子·尽心下》“万章问曰孔子在陈”章。
[611] 《论语·先进十一》:“过犹不及。”
[612] 《论语·雍也第六》:“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613] 韦伯,第121页。
[614] 埃斯卡拉,第74页。
[615] 《论语·雍也第六》“质胜文”章。
[616] 《论语·雍也第六》:“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人)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617] 《论语·泰伯第八》:“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618] 《论语·卫灵公十五》:“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619] 柏拉图(4),第740页。
[620] 《论语·述而第七》“述而不作”章和“我非生而知之”章。
[621] 柏拉图(3),第464页;(4),第739页;(4),第797—798页。
[622] 董,卷一,第2—4页。
[623] 《书》,第386、390、391页;《诗》,第509页。
[624] 郭沫若(2),34a、132a、133a、134b—135a。
[625] 《论语·为政第二》“子张问”章、《八佾第三》“周监于二代”章和《子罕第九》“麻冕”章。参看《盐铁论》(2),第79页。
[626] 《论语·八佾第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参看《礼记》,卷二,第324页。
[627] 《论语·卫灵公十五》:“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
[628] 《论语·八佾第三》:“夫子说:‘射箭并不在意射穿(靶)皮,因为人的力量是不同的。这是古旧的方法。’”(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但是,这种从强调力量到单纯强调技能的变更,不是我们应该在旧的军事贵族政治中预料到的东西,而更像是孔子取代纯军事观的总体努力中的一部分。支持这一观点的事实是《仪礼》(卷一,第95页)中的一句:“不射穿靶的箭,尽管它射中了,也是不记分的。”可是,同一本书在后文又使用了《论语》的文字,说:“根据礼,射箭不在意射中靶皮。”(《仪礼》卷一,第119页)《仪礼·乡射礼》:“礼,射不主皮。”
[629] 《孟子·尽心下》末章“由尧、舜至于……”。
[630] 顾颉刚(2),第135页。
[631] 《尚书·禹贡》,其成书于前儒家时期,是《书》中提到禹的唯一地方。
[632] 郭沫若(2),203b、247a。
[633] 《诗》,第622页。《论语·宪问十四》“南宫适问”章。
[634] 在孔子时代,“楷模帝王”的口头传说尚处在胚胎阶段,其证据来自这样的事实:比如,后稷这位周王室的神秘的远祖,《论语·宪问十四》“禹稷躬稼”章提到他“拥有帝位”。根据传说中的帝王世系,这是弄错年代的荒谬之语。
——译按:如果后稷是周人的始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他最终拥有了天下。这是一种传统观念,与弄错年代与否没有关系。对类似这种问题的理解,西方人士往往难于通融。
[635] 《论语·子罕第九》“子畏于匡”章;参见《子张十九》“卫公孙朝”章。
[636] 《论语·述而第七》“甚矣吾衰”章;参见《泰伯第八》“如有周公之才”章。
[637] 《孟子·滕文公上》:“周公、仲尼之道。”施赖奥克,103、110、134页。
[638] 《书》,第368、385、482页。
[639] 《书》,第496—497页。
[640] 西塞罗,第25页。
[641] 蒲鲁塔克,第344页。
[642] 《书》,第368、383、389—391、390、409、414、431、498—501页。
[643] 布赖斯,第66页。
[644] 《史记》,卷二,第170页。
——译按:《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645] 在《论语·季氏十六》“天下有道”章,孔子讲到了封建秩序,但与此同时他却倡导了一种比通常认为的封建主义更集权化的制度。这一章几乎可以肯定是后加的;见原书220—221页。
[646] 《论语·颜渊十二》:“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子贡:‘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647] ——译按:《韩非子·六反》:“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
[648] 《韩非子》,4.5b、16,5b—6a、16.10—11a、18.3b、18.10b—11a、18.12b、19.17b。
[649] ——译按:《论语·颜渊十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650] 《论语·为政第二》:“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651] 林赛,第240页。
[652] 柏拉图(3),第557—558页;柏拉图(4),第710页;亚里士多德,第1279页。
[653] 《论语·颜渊十二》“季康子问”章,即所谓的“康子三问”。
[654] 《论语·子张十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655] 柏拉图(4),第803页。
[656] 《论语·颜渊十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
[657] 《论语·公冶长第五》“子谓子产”章、《雍也第六》“子贡曰”章、《宪问十四》“子路问君子”章和《孟子·离娄下》“禹稷当平世”章。
[658] 《论语·子路十三》“子适卫”章。
[659] 《论语·里仁第四》“富与贵”章、“士志于道”章、《论语·述而第七》“富而可求”章、“饭疏食”章、《泰伯第八》“笃信好学”章、《先进十一》“季氏富于周公”章和《宪问十四》“贫而无怨”章。
[660] 《论语·雍也第六》:“君子周急不继富。”
[661] 柏拉图(4),第744、756页;亚里士多德,第1318页。
[662] 《论语·泰伯第八》:“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663] 注 。
[664] 《论语·述而第七》“自行束修”章、《子罕第九》“吾有知乎”章和《卫灵公十五》“有教无类”章。
[665] 伯恩斯,第176页。
[666] 很可能是,所有的孔子弟子一定程度上都具有贵族血统,尽管其中的一些人生活在受压迫的环境下。但孔子从未把出身作为一个条件,而结果是,即使不在孔子自己的时代也是在稍后的时代里,儒者群体逐渐地包含了纯粹是平民出身的人。
[667] 引自林赛,第135页。
[668] 见本书注 。
[669] 《老子》65章:“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译按:此处之“智”为多智巧伪诈之意。
[670] 《韩非子》,18.8b、19.8b—9a。
[671] 《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曰汤放桀”章、《离娄下》“储子曰”章和《告子下》“曹交问”章。
[672] 《论语·宪问十四》:“邦无道,危行言逊。”
——译按:孔子所说的“危行”,并不是大胆行动,而是“高行”,即在黑暗政治中持守节操,不去同流合污。
[673] 《论语·子罕第九:》:“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欤)?”
[674] 《孟子·公孙丑上》:“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675] 《论语·先进十一》“季子然问”章;参见《宪问十四》“子路问事君”章。
[676] 《论语·雍也第六》首章、“子谓仲弓”章和《先进十一》“从我于陈蔡”章。
[677] 西塞罗,第137页。
[678] 《论语·子路十三》“子贡问乡人皆好之”章和《卫灵公十五》“众恶之”章。
[679] 《论语·泰伯第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阳货十七》:“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680] 《论语·卫灵公十五》:“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译按:这一章的解释,恐怕不会有那么简单。严格来说,这一章中应该有些遗佚的文字,致使字义不明、意义不尽。
[681] 《史记·秦始皇本纪》:“皇帝躬圣……不懈于治……咸承圣志。”
[682] 《韩非子》,19.17b—18a。
[683] 《论语·子路十三》:“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又:“近者悦,远者来。”《宪问十四》:“上好礼,则民易使也。”以及“子路问君子”章。
[684] 柏拉图(4),第776—778页;亚里士多德,第1253—1255、1269、1279页。
[685] 韦慕廷,第11、237、241页。
[686] 《左传·昭公七年》;参看《孟子·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章;《国语》,1.6b—9a、4.9b—11a、5.10—11b、6.3a—7a。
[687] 郭沫若(3),第63—70页。郭氏在其他主张中表述道,尽管《论语》中的孔子不是无序政治的鼓吹者,但《墨子》和《庄子》却说他是,而在这三个凭据中应该少数服从多数。但是,这种算术式的证明,因为缺乏深究和权衡,几乎是不可接受的。一旦进行了深究,马上就会对郭氏提出的最严肃的证据做出结论,证明它们是非常不可靠的。郭氏关于孔子的那篇论文(同上,第63—92页)是一个重要的论述,像他的其他许多论著一样,它是卓越见识和广博学识的汇集,但经常令人失望地在材料的收集和使用中缺乏批判性的分析。在几个主要问题上,郭氏表述的观点与我这本书上的基本相似。为了不被指责为抄袭,我想指出的是,在我读到郭氏的那篇论文之前,我这部书的初稿已经基本完成,而在郭氏的那本书出版之前,我已经在我的教学中讲述了其中的许多观点。我很高兴能与郭氏的这些观点相伴而生,而他的这些观点又以其正确性而坚定了我的信心。
[688] 《史记》卷,第298页。
[689] 《论语·八佾第三》:“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
[690] 《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章、《论语·阳货十七》“公山弗扰以费叛”章。
[691] 《论语·阳货十七》“公山弗扰以费叛”章。
[692] 《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汤放桀”章。
[693] 《论语·子路十三》:“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亦见《为政第二》“季康子问”章、《里仁第四》“能以礼让为国”章、《颜渊十二》“季康子”章和《子路十三》“叶公问政”章。
[694] 柏拉图(3),第437、499—502页。
[695] 《论语·卫灵公十五》:“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参看《为政第二》首章。
[696] 《论语·颜渊十二》:“子夏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
[697] 《论语·为政第二》“哀公问”章、“季康子问”章,《颜渊十二》“樊迟问仁”章和《子路十三》“仲弓为季氏宰”章。
[698] 莱茵伯格,第130页。
[699] 孔子并不是第一个强调贤能之臣的重要性的,《诗》和《书》中出自周朝初年的材料对此已有提及。特别是周公,坚决主张任用贤臣的必要性。然而,很可能是通过孔子,这种思想才在后世获得了它的权威性。活跃在西元前300年左右、对中国政治理论具有极大影响的荀子,用历史实例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但是,当他总结自己的有关主张时却引用了据说是孔子的话语(《荀子》,第154—155页)。
[700] 《韩非子》,16.10b—11a、18.7b—8a、18.12b、19.7b—8a。
[701] 《论语·宪问十四》“卫灵公之无道”章。
[702] 《论语·先进十一》“子路使子羔为费宰”章。
[703] 《论语·八佾第三》“定公问”章,以及《宪问十四》:“忠焉,能勿诲乎?”
[704] 《论语·子路十三》“定公问”章,以及《宪问十四》:“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705] 《论语·八佾第三》首两章、“管仲之器”章,《述而第七》“奢则不逊”章和《宪问十四》“臧武仲”章。从《泰伯第八》(亦见《宪问十四》)“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及《宪问十四》“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来看,孔子谴责了那些不在官位者对政府的批评。但令人不可理解的是,一个像他那样崇尚自由批评的人竟然会有这种看法。看起来,这些表述是在我们不可得知的特殊参照系下讲说出来的。
——译按:“谋”和“思”并非批评;特别是“谋”,显然是指别有用心地参与不符合自己身份的政治谋划。正如本书作者强调的,孔子批评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而是无道的政府作为。
[706] 林赛,第284页。
[707] 《论语·颜渊十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此和《子路十三》的“正名”为基础,产生了孔子对“正名”学说的详细阐述。但《子路十三》的这一章有许多疑点,显然是后来插入的,可能是受了法家的影响。见本书注 。“君君臣臣”的观念与“正名”思想并没有必然联系。因为《论语》中只有这一章讲到了“正名”,明显是靠不住的,所以,并没有证据表明孔子了解这一学说。
——译按:对于《论语》中的章节,不宜如此随意地下断语,更不能说只讲过一次或讲得很少的观点就是靠不住的。如果解释者不能理解的章节都是可疑的,那么,任何典籍都将无法卒读。事实上,“正名”思想正是《论语》中孔子思想的主线之一。
[708] 《论语·为政第二》:“君子不器。”
[709] 《论语·卫灵公十五》“直哉史鱼”章,参见《述而第七》“子谓颜渊”章和《泰伯第八》“笃信好学”章。
[710] 《论语·为政第二》“非其鬼而祭”章、《宪问十四》“子路问成人”章、《卫灵公十五》“志士仁人”章和《子张十九》首章。
[711] 汤,第159—161页。
[712] 柏拉图(3),第496—497页。比较《论语·宪问十四》“邦有道”章、《卫灵公十五》“直哉史鱼”章和《子张十九》“陈子禽谓子贡”章。
[713] 《荀子·君道》:“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
[714] 亚里士多德,第1287页。
[715] 《韩非子》,18.7b—8a、18.12b、19.7a—8b。
[716] 《左传》的一章渲染了孔子对法律的看法。这一章引述了孔子反对公布法律的话语,其主要理由是,把法律向社会公开就会破坏社会的等级分层,比如他问道:“贵贱不分之时,国家怎能管理?”(《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贵贱无序,何以为国?”)这听上去根本不像是孔子说的话。另一方面,它的内容显然有似乎孔子出生后15年晋国叔向所写的一封信中讲述的观点。(《昭公六年》)把这样的观点归之于孔子是很成问题的。
[717] 莱茵伯格,第5页。
[718] 亚里士多德,第1287页。
[719] 林赛,第54—55页。
[720] 雷丁,第502页。
[721] 温德尔班克,第171—173页。
[722] 梅里亚姆,第50—70页。
[723] 亚里士多德,第1289页。
[724] 梅里亚姆,第11—12页。他指出,这些表述中的第一条,部分地是从德尔克海姆那里改写过来的。
[725] 哈特斯利,第154页。
[726] 康德(2),第24、27页。
[727] 哈特斯利,第240页。
[728] 林赛,第281页。
[729] 梅里亚姆,第19页。
[730] 霍尔库姆,第171—172页。
[731] 伯恩(2),第187页。
[732] 芬纳,第22—23页。
[733] 《论语·卫灵公十五》:“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734] 《论语·颜渊十二》“季康子问”章和《子路十三》“善人为邦百年”章。
[735] 芬纳,第35页。
[736] 《论语·卫灵公十五》:“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737] 林赛,第121页。
[738] 引自林赛,第124页。
[739] 《论语·颜渊十二》:“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参见《为政第二》“道之以政”章和《子路十三》“善人为邦百年”章。
[740] 《论语·里仁第四》:“朝闻道,夕死可矣。”
[741] 《论语·雍也第六》:“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742] 林赛,第60页。
[743] 伯恩(2),第234页。
[744] 《孟子·公孙丑上》。
[745] 例如,《墨子·耕柱》:“墨子对骆滑厘说:‘我听说你喜爱勇猛(之士)。’骆回答说:‘是的。不论何时,我只要听说某个地方有个勇士,就一定得去杀了他。’”(“吾闻子好勇”,“然。我闻其乡有勇士焉,吾必从而杀之”。)
[746] 《国语》卷十五。
——译按:董安于曰:“今臣一旦为狂疾,而曰必赏女(汝)。”
[747] 《论语·颜渊十二》“子贡问政”章,《子路十三》“善人教民”章、“以不教民战”章,《宪问十四》“陈成子弑简公”章以及《左传·哀公十四年》。
[748] 关于“儒”的原意,胡适和冯友兰有两种不同的理论,详见胡(5)第3—81页和冯(3)第1—61页的长篇之论。我自己的结论部分地(仅仅是部分地)与他们每个人相一致。胡氏和冯氏都同意汉字“儒”有“懦弱”之意,而冯氏认为,它指的是学者们,因为他们不喜欢战争。说“儒”曾经是贬义词,这可能只有少量的证据,但是,自从它不久就变成社会中最体面阶层的名称之后,这种贬义就不太受人注意了。有多少基督徒还知道罗马帝国的十字形是恐怖和堕落的象征呢?在《左传·哀公二十一年》中,“儒”曾被用为非难之词(“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而韦利(第239页)认为“儒”是给傲慢不恭的鲁国人所起的诨名,因为他们有“绥靖”的特性。《礼记》(卷二,第409—410页)引述孔子的话说,“儒”这个词被错误地用于污辱人,而鲁哀公则告诉孔子:“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把它用作贬义词。”(《礼记·儒行》记鲁哀公语曰:“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这次谈话是完全不足凭信的。但是,对于这样的表述,有一种不太充分的解释是:之所以在像《礼记》这样的可敬的儒书中出现这些说法,除非在某一时候,“儒”确实被当作贬义词使用过。
[749] 在《论语》中它只出现在《雍也第六》“子谓子夏”章,在《孟子》中它只出现过两次(《滕文公上》“墨者夷之”章和《尽心下》“逃墨必归于杨”章),出自孟子本人口中只有一次。尽管墨子生活在孟子之前,他却更多地使用这个词并认为孔子是“儒”(《墨子·公孟》);这还不能确定是否是因为他对儒家集群持批判态度。可是,《墨子》的《非儒》篇却是后来的作品,见本书注 。
儒学
第十一章 “懦弱者”
“儒”——“懦弱者”——这个词,通常译为Confucians,即儒者或儒生,我们将遵从这个惯例。在中国,人们很少用孔子的名字(Confucius)来称谓他的学派。 [1] 不过,在孔子时代,对“儒家”来讲,或者说对以孔子为首的这个社会集群来说,“儒”显然并不是个流行的称谓。但是,在孔子之后不久,这个称谓就变得很流行了。
人们通常认为,儒学在西元前2世纪取得了胜利。但它并不是没有荣枯盛衰就达到了这一步,而是像任何一个经历了多次战役的老兵一样,伤痕累累。另一方面,它的3个世纪的奋斗结果也并不是它当初的追求。同样地,流传下来的孔子思想也经历了极大的变更。
孔子去世后的3个世纪,对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这30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历史时期。这是个经历了最彻底的变化的时代,几乎每一样东西都从它的旧的依附处逃逸出来。人们的社会地位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升降起落。交通状况极大地改善,人们可以前所未有地四处旅行。货币已经流通,商业发展到了可观的程度,而私人对土地的占有逐渐取代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形式。战争达到了新的规模和新的恐怖程度。从政治上讲,在孔子时代近乎达到其高潮的分权的潮流逆转而下。强国以一种逐渐增加的速度征服和蚕食他们的邻国。某些已经篡夺了国君实权的大家族,接着又夺取了君位。这些家族一旦登上君位,就更着意于发展强大的政府机构,以预防别人取代他们。新上台的贵族们发现,稳固其权力的较妥帖的办法是,不要把权力交给自己的亲戚和其他有势力的贵族,而是去大胆地任用那些出身相对贫贱的人,通过训练,让这些人掌握管理政府的才能,处理大大小小的政治事务。
如前所述,即使是孔子,都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权力机构去取代周天子 [2] (这个凄惨的傀儡)来统治全中国。人们已经达成的共识是,新的王朝一定会到来。而唯一的问题是,谁来建立这个新朝代?几乎所有较为强大的诸侯国的君主都用贪婪的目光盯着尊贵的王座,并且为这场大较量而组织他们的国家、训练他们的武装。
有人可能会认为,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没有人会有时间光顾哲学。但情况恰好相反。各国君主四处寻找哲学家,并对他们殷勤招待,以至于显得哲学家们在任何地方都很难得。甚至是秦始皇这位极权君主,尽管曾下令焚烧书籍并力图在除了他的官员以外的所有人中禁止学习哲学,但是,根据记载,却在读了哲学家韩非子的两篇文章之后说:“啊呀!如果我能见到此人,并与他结识,我将死而无憾。” [3]
君主们之所以具有这种兴趣,从根本上讲并不是想要进行纯文化的追求。中国哲学的传统是,首先关切人类的实际需求,全身心地考虑伦理的和政治的问题。哲学家们坚持不懈的观点是,如果一个君主掌握了适当的哲学,就能控制整个中国。比如说,孟子和荀子这两位最著名的早期儒生都曾断言,一个把儒家原理付诸实施并任用儒者管理其政府的君主,肯定会统治全国。 [4] 他们的对手否认这一点,但同时却也宣称,只有他们的哲学才真正具有这样的效力。
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哲学“学派”的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这种分法对于帮助人们区分不同的思想流派是有用处的,但是,正如许多学者认识到的,它也会使人产生误解,即容易使人认为每种思想都是一个牢固的和有组织的集团。在汉代以前,只有墨家才形成了这样的集团。人并不是可以分别归档的文件。尽管多半人无疑把自己看作是显著地属于某种思想传统或另一种,但事实却是,每一种思想传统都受到了所有其他思想的影响。因此,我们便在那些被认为是纯儒学的著作中发现了大量的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反过来讲,儒学也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学派的哲学。
之所以有各种思想流派的思想相互混杂,并不仅仅是由于全部思想流派的思想对思想家个人思想的影响所致。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从内容上进行渗透和破坏的形式,其方法是:直接把外来章节插入到某一书中,以期影响或改变某一学派的思想形态。我们已经看到的,并且将要更多地看到的是,在《论语》中就有许多被窜改过的痕迹和非儒家的思想观点的插入。胡适指出,被称作《墨子》的这部书的开头三章“没有任何墨家精神”, [5] 实际上,它们很可能是儒生对其原文的增补。这种外来物是司空见惯的,甚至出现在每个学派的代表作中。此种状况显然造成了一些复杂的情形。然而,尽管要把各个学派作一基本区分的工作困难重重,但并不是毫无希望的。每个学派毕竟还都有其确定的主要原则,围绕着这种原则,每一派哲学就可以被系统地组织起来。同时,对于各个学派的原典,尽管人们从未能完全予以澄清,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可能发现其中的附加物或外来的异物,因为,这些附加物或异物与它们所攀附的著作的主导原则是不相同的。可以说,即使我们只是想理解这300年间各派思想发展的概貌,也非常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同时,即使我们只想探究儒学的发展和孔子思想的蜕变,我们也必须了解其中的种种奥妙。
如前所述,孔子在世时,弟子间就产生了许多显著的思想分歧,尽管还不至于说是争吵不休。但是,一旦孔子的权威因为他本人的去世而有所变动,这些分歧就一定会变得非常突出了。孟子说,孔子弟子们有过让弟子有若做孔子继承人的意图,但并没有成功。 [6] 韩非子说,儒家逐渐分为8派,并且“每一派都坚持认为独自继承了真正的儒家传统”。 [7] 《史记》记述道:“孔子去世后,他的70位弟子四散周游到诸侯中间。其中最有成就的成了(国君的)教师或大臣;差一些的做了官员们的朋友和教师,或者隐而退之,再也不为世人所见。”有4位子夏的弟子据说“都成了君王的导师”。子夏自己则是魏君(文侯)的私人教师。 [8] 孟子又说,有两位早期的儒生是国家的大臣,其中的一位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他大抵先后做过两个国家的大臣。 [9]
孟子引述孔子的这位孙子(子思)的话说,他告诉鲁穆公,国君只能服侍学者们而不能自以为是地跟他们交朋友。显然,学者们已经开始了扭转世袭贵族政治地位的发展进程,并要求“把他们安置在各自的位置上”。孟子说:“学者们劝说那些大人物,但却藐视他们。” [10] 荀子宣称,真正的君子“是与天地平等的”;并且还说,尽管一位大儒可能会相当穷困,然而,“王公大人却无法和他争夺名望”。 [11]
孟子相信,如果是根据德行来决定的话,他自己就应当成为天子。 [12] 但是,既然没有这个机会,孟子就发展出一种酸葡萄哲学,硬要说真君子从中可以取乐的东西“是世间的君王没地方去找的”。 [13] 于是,孟子就与其他儒者一道,倡导另一种观念,即:他们是属于至高无上的那类人。虽说他们倒是可以通过做官而屈尊就驾地帮助君主,但最惬意的还是去做一个仅仅是自由发表批评意见的顾问,用他们的忠告收取报酬,而只担负些无关痛痒的责任。
对儒者来说,所有这一切无疑是很愉快的。但是,我们不得不问,统治者为什么要忍耐儒生的这种行为呢?为什么那些为所欲为、一时兴起就可以把人碾为齑粉的暴君,不仅允许儒者宣讲革命, [14] 接受他们的致命攻击,还得请求他们不要离去呢?有一个原因我们已经指出过,这些君主们希望儒生能有助于他们进行一统天下的斗争。而且,时代正在变革,在当时中国的东北部(大部分儒生是在那里进行活动的),至少人民正在变得日益有教养和思想开放了。从理论上讲,无论君主拥有怎样的专横权力,他们都不能安稳地压迫臣民而不顾及超过某种极限。同时,儒生们则认为,政府即使不是民主的,至少也应该是仁慈的。这是一种可以指导实际运作的政治哲学。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在前文已经讲过的原因,那就是,儒者,并且显然只有他们,拥有为政府机构训练人员的成套规则。当然,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标准相比,这样的规则可能是初步的,但它显然要比什么都没有强。
无论由于什么原因,相互竞争的君主们最终获得了儒生的服务或忠告。事实上,各个派别的多种多样的学者和哲学家都被统治阶层殷勤以待,有吃有喝。据说,孟子“有几十辆车和几百人跟随他周游列国,诸侯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招待他”。孟子住在宫殿里,还得到了君主们大量的金钱馈赠。 [15] 人们特别指出,西元前322—前314年在位的齐宣王(到那时,有一些国君已经自称为王)就是哲学的赞助者。一位汉代的作者说,齐宣王集聚起了1000多位学者,而像孟子那样的人“得到的是高级官员的薪俸,不承担官职上的责任,却可以参议国家事务”。 [16] 《史记》补充说,齐宣王为这些哲学家建造了巍峨的公馆,给他们以最高的待遇,以此来吸引他们。 [17] 在随后的世纪里,法家的韩非子宣称,君主们把财富和地位过度慷慨地给予了毫无实用价值的学者,以至于没有人想去做实实在在的工作了。 [18]
孔子显然对人的品格有良好的判断,并对他的弟子提出了很高的道德品质标准。然而,即使在孔子弟子中也有懒惰者、不诚实者和贪图金钱者。在孔子死后的几个世纪里,整个儒家集团的才智和品格的平均水平一定有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在孔子之前,要达到高层社会地位几乎只有唯一的一条途径,即出身于那个阶层。但现在却不同了,一个出身最卑贱的人,如果具备了广博的学识和伶牙俐齿,就有希望居宫室、衣狐裘、拥美妾,获得最高的社会地位,享受最高的生活待遇。即使他不能做国君,也可以成为宰相;如果他是充分有才能的人,至少还可以获得不受处罚地轻视和攻讦国君的满足。
韩非子问道,如果依靠一定的学识和机敏的谈话,人们就可以不用劳苦、不冒风险地得到财富和荣耀,“那么,还有谁会不愿意得到呢”? [19] 到底是谁呢?有一本书告诉我们,人们毫不犹豫地乘车或步行几百里去跟随那些出了名的老师学习。 [20]
这样一来,如下的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许多可以被称为儒生的人是孔子为之自豪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学者,但也有许多儒生对物质享乐和贪图名利更感兴趣。要想了解这一点,我们不必只看儒家敌手的书,即使是儒家的书籍就告诉了我们许多。孟子说,在他的时代,人们修养品格只是为达于高位,而一旦取得成功,他们便抛弃了自己的原则,因为不再需要了。 [21] 自己也是儒者的荀子,却对那些被他称作“俗儒(庸俗的儒生)”的人物进行了刻薄的谴责。荀子说,他们讲究的是穿着特别的衣帽,他们的学识是肤浅和混乱的,在衣着和行为上“与世俗流行的相一致”,他们“谈论先王以便欺骗蠢人并得到衣食”,他们活得就像君主的宠臣和家臣们的食客。 [22] 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在一章中这样讲:“现在有许多称为‘儒生’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儒者。” [23]
儒者的敌手非常严厉地谴责全体儒生,但是,这种攻击通常是出自明显的恶意,很难让人信服。可是,的确也有那么一大批儒生,他们的令人吃惊的表现却不能使人为之自豪。那些类似于“俗儒”的人并不在少数。当任何职业变得容易得到并有利可图之时,它就会吸引一些像“叼腐肉的兀鹰”一般的渣滓。那么,他们是怎样过活的呢?在他们之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具有做一个成功的教师或政治家的素质。《墨子》中有一章确实是晚于墨子本人的资料, [24] 但却没有人不对它感兴趣。它是这样描写一个儒生的:
对吃喝很贪婪但却懒于工作,在寒冷和饥饿的危险中忍饥挨冻。……在春天和夏天,他去乞食麦子。收获之后,就专心于丧礼。儿孙们和他在一起,吃喝都能满足。他只需要去主持一些丧礼……当他听到富人家死了人的消息,就大喜过望地说:“这可是得到衣服和食物的机会啊!” [25]
这当然是一段颇有恶意的讽刺文章,然而,其中无疑也透露出一些真情。我们已经看到,孔子本人和某些弟子对于适宜的礼仪演示给予了极大的注意,还探讨过这种礼仪过程中的细微之处。在《礼记》中,特别是称作《檀弓》的那部分,有大量的关于如何举行丧葬之礼的细枝末节的记录,有人就此认为,其中的一些内容是孔子和弟子们的陈述。这种认定当然是很可疑的,但这些著述确实反映了儒者的利益。因为,在古代中国并没有职业祭司,而儒者却精通礼仪,所以,人们有理由认为,许多能力较差而又需要辛辛苦苦地维持生计的儒生,就得依靠为人家主持丧礼而得到一些收入。
所有这些根本不是孔子当初的意图。孔子特别告诫人们,不要只是注意礼的形式而忽视了它的精神实质。孔子还谴责了这样的人:他们借口专心于大道,但真正关心的却是个人的享乐和幸福。 [26] 不过,对于他的众多后继者的堕落,孔子不能完全不负任何责任。但是,只因为孔子坚持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教育而责怪他,这可能也是不公正的。孔子仅仅是在倡导自由的受教育渠道。但毫无疑问的是,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使得后儒难于彻底实行挑选合适学生的“入学资格”。
孔子创立的这种教育体制的确从未造就出另一个孔子,这使得有人认为,孔子的这种新的教育体制是他的一项更为严重的失误。孔子自己年轻时不得不去努力奋争,从头做起,这样的经历无疑是对他的造就。孔子在卑贱的环境下长大成人,并且从未丧失过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柏拉图指出,波斯人大流士(Darius)之所以伟大,是由于他“不是国王之子,并且没有受过奢华的高等教育”。 [27] 而在古代中国,人们也经常做出这种有益的评论。孟子就说:“有德行和有才能的人,总是要经历磨难和度过艰苦的生活。” [28] 可是,孔子并不欣赏这种观点。孔子认为,自己早年的奋争并不重要,不值一提。孔子所倡导的教育过分地关注于政治技能和政治哲学以及从政的生活,并努力要把他的学生从像他那样生活的人们之中拉出来。 [29] 也就是说,一个不同寻常的年轻人,在适宜的环境下接受教育,并深信自己注定要成大器,这才能使自己避免成为小人。作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伟大的教师,孔子能够使他的学生做到这一点。但是,在孔子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像孔子那样严格地按照他制定的原则行事了。
如果要说所有的儒者或者一定程度上像儒者的人都是目光短浅的、徒有其表的和追逐私利的,那将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异常豪放、有学识和大公无私的。但是,这种人从来都不是任何较大的人类集群的主体。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像孟子和荀子所认为的那样)伟大的儒者并不多见,而更多的是普通儒者的话,就会限制我们深入到儒学内部对儒学进行理解。大量的寻常儒生既无智慧亦无能力著书立说,而当他们要去著书时,所写出的书也不会比《礼记》和《易》“十翼”中的粗俗乏味的那些部分更高明。我们读到的这些后来写成的著述在数量上是《孟子》和《荀子》的十倍或者百倍, [30] 但是,它们给我们的印象是,这些后来的东西与真正的儒家思想明显相反。尽管一个单独的寻常之人不如一个单个的天才人物有影响,但是,如果把许多寻常之人的影响力聚合起来,却具有压倒性的势力。这些寻常之辈所营造的文化环境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他们时代里的精神巨匠,同时,他们还不断地改变和曲解孔子的原则,使它成为被那些理解力有限的人更容易接受和更便于使用的东西。他们对于真正的孔子知之甚少,而更多的是用有意创制的和精心装饰的传统说法弥补他们的这种缺陷。当他们去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地把孔子描绘得很像他们自己,或者像他们所钦佩的那种人,即:有权力的、受人奉承的、赶时髦的、有时更是狡诈的人。我们一定要简略地探索一下这个传统的发展线索。为此,我们也将不得不考虑与儒学相对立的那些思想派别。
第十二章 从人到神
墨子出生在孔子刚去世之后,他创立的哲学是著名的墨学,创建的组织严密的团体是众所周知的墨家。在那时,墨学和墨家团体都是重要的力量,但是,到了汉代,它们却彻底崩溃,并最终消失了。像孔子一样,墨子确实被由于贫穷、无序和战争所引起的普遍的灾难震惊,他也四处周游,传布他的纠正这种状况的方法。近年来有一种相当常见的看法是,中国人的严重缺陷是在于更偏爱孔子的而不是墨子的学说。虽然我们眼下的任务不是详细描述或再次评判墨子的思想,可我们还是得说,墨子传给我们的学说显示出严重的理性上的或者学理上的不足。墨子对儒生和其他人的批评通常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反对宿命论的主张,比如“命运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人曾听到或见到过命运”等说法,却简直没有哲学家的风范。他的消除战争的办法是,“当诸侯们互相喜爱时就不会再有战争了”,这并不是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为了让一个年轻人成为他的学生,墨子先向这个人许诺,说可以让他得到像样的社会地位,但后来又告诉人家,他之所以许此诺言,仅仅是一种骗人的手段,以便让人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跟他学习,这种做法从道德上讲也是令人怀疑的。 [31]
被称作《墨子》的这部书包含了一些出自后人之手的材料,而其中的一些人甚至都不是墨者,但是,人们可能有一定的把握分离出这些外来的东西。 [32] 留下来的部分也许可以为我们当代人描绘出孔子刚去世后那一时期的中国思想界的情形。据说墨子曾经是一位儒生, [33] 但后来与儒家决裂并创建了自己的团体。为强调他的独立性,墨子激烈地批评儒生。但是,在构成墨子学说的广阔基础中,事实上大部分是他那个时代的儒学。从墨子所攻击的观点以及他所能接受的那些观点中,我们了解到了这一点。
墨子谴责宿命论,断定这是儒家的学说。 [34] 如前所述,我们很难确切地说孔子是个宿命论者,但是,这种学说可能在孔子死后的儒家集群中得到了发展。墨子也抨击厚葬的做法,认为厚葬的结果是,“普通人的死会耗尽一家的财产,诸侯之死将用光一国的财富”。 [35] 在这一点上,孔子显然与墨子是一致的。但是,根据墨子对厚葬的批评,在墨子的时代,儒生之间已经产生了思想分化。 [36] 可是,如果“俗儒”靠主持葬礼过活的做法真的是可以理解的话,他们就会赞成奢华的丧葬费用,而到了荀子的时代,大力抨击“俗儒”的荀子也为厚葬进行辩护。 [37]
我们从《墨子》中得到的印象是,那时的儒生特别着意于模仿某种古代的风格,这表现在衣着上,也表现在其他方面,以至于使他们成为对过去的奴性效仿者。在一个国君的宫廷里,一位儒生“只是在问他的观点时才讲话”。 [38] 我们并不希望身为儒家敌对派别领袖的墨子会选择最好的儒生来描述儒家,但无可怀疑的是,此时的儒家内部恰恰出现了太多这样的人,他们对真正的儒家原则缺乏了解或不太关心,但却渴望获得美好的政治前程。
《墨子》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非儒》(反对儒生)。这篇文章谴责了整个儒家集群,并包含了对孔子的粗暴攻击。例如,它把孔子在世前的某个时期发生的盗窃案记在了孔子某位弟子的名下,表现出了最显眼的历史舛误,而整个这篇文章在文笔和内容上又不同于《墨子》一书的其余部分。正如梅贻宝所认为的,它无疑是“写成于很晚的时期”, [39] 并被增补进了《墨子》原初部分之中。在《墨子》中比较可靠的篇章里,墨子很少提及孔子本人。在几乎是唯一的描述性的一节中,墨子把孔子归在愚人之列。 [40]
墨子相信,在如何医治世界之疾病的问题上,他比任何其他人都知道得多。因此,墨子与孔子不一样,不情愿留下任何让其他人自己进行选择或判断的余地。引述墨子的话就是:“我的学说是有效的。要舍弃我的学说而企图去想他自己的,就是抛弃整个收成而去捡几粒谷子。” [41] 墨子进而认为,没有别的人可以驳倒他的学说。因此,在他的学派中,墨子把学生置于铁的纪律之下,并要求他们毕生从命。有人认为,墨家团体的领袖(其职位是传承的)掌握着对其成员的生死之权。 [42] 墨子相信,这个世界的种种灾病,包括贫穷、无序和战争,可以由严格的独裁主义式的组织去医治。在每个团体或阶层中,所有成员都应该“与领袖保持一致”,而每个次一级的团体或阶层的领袖必须依次与他的上司保持一致,直到天子为止。“在上者认为是对的,所有人必须认为是对的;在上者认为是错的,所有人必须认为是错的。”那些不遵从上司的人应该受到惩罚。 [43] 把这一观点与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所声称的主张作一比较是很有趣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要想使整个国家机制能够成立,其原则必须是:每个领导人对下行使其权威、对上尽到其责任。” [44]
但是,怎样才能保证那至高无上的领袖、天子具有正当的原则和纯洁的动机呢?答案是,天子一定得依次与上天保持一致。但又怎能知道他是否这样做了呢?叫墨子来说,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如果天子不按照正确的原则行事,那么,“天就会无节制地降下冷冻和炎热,还会伴有不合时令的雪、霜、雨和露。五谷不会成熟,六畜也不发育;疾病、瘟疫和灾祸就会流行。不断的飓风和水灾的祸害是上天对那些不与它保持一致的在下之人的惩罚”。根据墨子的说法,上天不高兴时的表现有时确实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那就是“像下雨一样下三天血,龙也出现在庙堂里”,以及其他等。 [45] 墨子引用许多诸如此类的事件来支撑他的主张,并声称这种事件是有历史根据的。这类奇异之事可能并不是墨子杜撰的,而是墨子利用了大批受公众欢迎的民间传说或其他的有关说法。
对当今之人来说,上面的那些说法听上去颇为滑稽,而很可能对孔子来讲更是这样。墨子本人谴责了儒家对于鬼神之存在的否定,而他则是虔诚地相信鬼神的。 [46] 不过,墨子的关于自然灾害的出现乃是天罚并指示出存在着一个邪恶政府的思想,以近乎同样(尽管更精致)的形式出现在汉朝的所谓正统儒学之中。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说墨子直接影响了儒学,那是令人怀疑的。所以,更可能的历史脉络是:先是墨学,接着还有儒学,两者都受到了大量世俗迷信的影响。这些迷信思想远比孔子的理性哲学更受普通人的欢迎。
一般认为,孔子把他的相当大的思想重点放在了古书的权威上,并确定了“古代圣王的榜样”。不过,《论语》对这样的思想并没有什么支持。反倒是墨子却不断地引用书本和圣王来论证他的主张。墨子宣称:“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相一致的所有言行,都应该履践。而与三代邪恶之王……相一致的所有言行都应该舍弃。” [47] 很难想象《论语》中的孔子对于人的行为会定下这种独裁性的衡量标准。另一方面,人们也没有理由相信,墨子与同代的儒生,即那些使墨子得到早期教育的人,在这方面会有什么大的不同。
孔子提出的是思考问题的原则而不是真理的恒定标准。他给个人规定的责任是,寻求他们自己的真理,并为此而自由行事。但总的来说,人们并不期望得到理性的自由,因为这必然要求脑力的劳作。有人已经指出,即使在今天,在我们中间,“无论什么阶层、什么职业的人(包括大多数哲学家)都想得到这样的哲学:它们将是一下子建成的一个封闭体系,讲述的是有关个人和宇宙的所有终极性质和最后的定数”。 [48] 可是,孔子给人的心灵提供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令人深感惊奇的是,究竟是没有多少弟子能够很好地理解孔子的思想呢,还是在孔子尸骨未寒之时儒生们就开始建立他们的温馨的理性避难所(他们在其中找到了圣典和一贯正确的圣人们的令人欣慰的权威)呢?
关于早期圣王的传说迅速地成倍增加。我们在《论语》中看到的尧、舜和禹是作为古代贤明国王而出现的。但是(除了这本书的最后一篇,一般认为是后来的,而我们将在下文讨论它),除了大禹之外,《论语》中并没有说尧和舜是以非正常的形式(即“禅让”)成为国王的。 [49] 大禹被认为曾是农夫,但在某些地方也隐隐约约地认为他是皇室之后。《论语》宣称,任用大臣的时候,应该根据他们的德行从全体人民之中选拔,并说古代就是这么做的。 [50] 根据逻辑推论,下一步就应该认为,国王也不应该是世袭的,而是应该根据其德行和才能来选拔。孔子无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只可惜没有明确的记载来证明孔子直接地如此表述过。而在墨子这一代人当中,却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根据这一代人的说法,在古代圣王的时代,统治者以德行和才能为基础在全体人民中选择他的继承人是很正常的。学者们用这种学说完全改变了世袭贵族的处境,并最终告诉这样的贵族说,他们的王位不过是篡夺而来的,因为按理说,王位应该属于有才能和有德行的学者。
【按:其实当时人都是亲戚关系,祖上都能追溯到伏羲、炎帝、黄帝等,血统自然不能成为最重要的条件。 】
《墨子》一书最早表述了这一学说。因为这一原因以及其他理由,有人认为,这一学说是出于墨子的,但这未必是真实的。 [51] 墨子自己确实有过这样的观点,但是,他也引用了儒生的如下说法:“从前,圣王排列地位时,规定至圣之人做天子,其余的根据其美德往下排列,顺序担任大臣和高级官员。现在,孔子广泛精通诗和历史文献,鉴别了礼和乐,并拥有对所有事物的详尽知识。如果孔子生活在圣王的时代,他一定会被奉为天子。” [52] 孟子后来也说过几乎是同样的事情。 [53] 公平地说,关于古代圣王并非世袭王位、而是只能依靠他们的德行得到王位的思想,显然是产生于孔子死后不久 [54] ,并被儒家和墨家共同采纳的。
不过,某些儒生却是很谨慎地看待这种观点的。作为一种提高儒家学者之威望的宣传来讲,这种观点是很精致的,但是,如果贵族们过分认真地看待它,那么,对于倡导它的儒者来说是会有麻烦的。即使在今天,某些相当民主的人士还很欣赏立宪世袭君主制,认为这种体制具有政治稳定性。也有人认为,如果统治者四处寻找有道德的个人并给予他们王位,就很容易使那些最善于言谈的人戴上王冠,而现实政治就会出现混乱。这种糟糕的事情确实于西元前314年在燕国发生了。 [55]
作为古代圣王“禅让”传说的发展,有人声称,圣王在他们年迈之时让位给了有道德的大臣。在燕国,据说是国君要把国家交给他的相国(这个建议来自于这位相国的一个亲戚,此人是受了贿赂的)。国君做出了“禅让”王位的郑重宣布,这位相国表面上予以拒绝,但事实上却接受了。三年之后,燕国发生了暴乱,“几万人丧了命”。 [56]
孟子批评了燕国君主的弃国之举, [57] 并宣称只有上天才有权把国家给予不是世袭的王位继承者的那个人。孟子认为,只有人民接受这个人作为他们的国君,才是真正的天授王位。 [58] 荀子认为,在古代,官位是根据德行来任命的,为此,帝王死后,王位有时就不再属于帝王之家了,但他否认圣王在活着的时候就禅让了。 [59] 较晚一些时候的汉文帝(德效骞Homer. H. Dubs认为他的统治标志着“儒家影响”在汉代的开始 [60] )把这种传说牢记在心。西元前179年,汉文帝发布诏书说,他完全应该“在整个帝国广泛地寻找一个有才能的、贤明的和有德行的人,好让他自己让出王位”。他说,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让他的儿子做他的继承人。可是,大臣们表示反对。他们(成功地)坚持认为,帝国的稳定只有依靠维护王位的世袭传承。 [61]
儒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能够遵循选贤任能的原则任命大臣,就必然会产生良好的政府。儒家学者坚持认为,这种选才思想,过去的君主曾经拥有过,当今的君主也都应该具备。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极大地提高了儒家学者们的威望。况且,这种思想也是对君主们可能会有的蛮干冲动的最有效的心理约束,因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这些专制君主们就能够成为专横的暴君。但是,如果这种思想真的被付诸实施,将会使王位成为最残暴的阴谋家的玩物。而且,如果一个专制君主相信他之所以得到王位是由于他的才智和德行,那么,与那种受过儒家思想之适当教育的世袭君主相比,这个专制君主就会更专横,更缺乏对理性的服从。因此,毋庸置疑,最有智慧的儒者一心要保持的把王位留给有德有才者的原则,只能被作为历史上的一个美丽而遥远的景观来保存了。
显而易见,所谓让有德者继位的说法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在古代中国,直到非常接近于孔子的时代,都很难让人相信一个平民出身的人会得到提拔,甚至去做高官,更不用说成为国君了。 [62] 另一方面,却有大量证据表明,重要的官职一般来讲都是在贵族世家中传承的。 [63] 但是,当学者们提出在古代是有德者做国君的观点时,他们就得提供能够证明此种观点的历史文献。和平常一样,需求刺激了供给。没过多久,就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证明了这一点。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尧典》,而这篇文章(至少其初稿)显然是写成于孔子死后150年中的某个时期。 [64] 甚至在《论语》中,比如最后一篇的第一章,也被插入了一些有关尧、舜和禹相承传的语句。但是,这类说法与孔子毫无关系,并且很久以来就被认为是《论语》的外加部分。
很显然,在古代中国,至少早在周朝初年就有人开始写作伪书了。 [65] 但是,直到孔子去世后不久,这种伪作才开始光芒四射。到了孟子时代,竟然有了那么多可疑的书,以至于孟子说:“就是没有这些历史文献,(怀疑他们)也比全信它们的好。” [66] 然而,书籍的伪造者还是忙个不停,并且开始返回头来撰写那些被认为是历史上有过的书籍,其中一些书籍记载的是传说中所说的过去发生的各种事情,以及各种乌托邦式的空幻思想——这些都是他们期望在未来得以实现的东西。比如在《尚书》这本书中,只有四分之一的文献确实是写成于它们所说的那个时候,而其余的便都是伪造的了。对某些别的书籍来说,情形则更糟。因此,古代中国历史成了事实与虚构组合而成的大杂烩,其中固然有其辉煌灿烂的一面,但也有其近乎不堪造就的另一面。对这个庞然大物进行科学的学术研究尽管只是最近才开始的事情,但却在区分整理基本史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因为有了对孔子的如此理解,就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不仅有关他的生平和思想被完全歪曲了,更糟的是,他在世时的整个历史背景也已被伪造,以至于不可能正确地看到孔子这个人了。据称,在上古时代,得到王位的人靠的不是继承权而是德行,然而,孔子从未明确说过这种事情就是实情。总体来看,有许多事情想要说明的是,孔子信奉世袭原则(世卿世禄)。然而,事实上孔子不仅不信奉这种原则,而且还更加大胆地向前跨进了一步,坚持认为对于最高阶层的大臣的任命,应该根据他们的德行和才能,而不是他们的出身。
孟子出生在西元前400年后不久,大约孔子去世后一个世纪的时候。据说,孟子曾经跟随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弟子学习过。 [67] 在所有那些有思想流传下来的儒者之中,孟子是最早的一位,而且,我们有理由认为,传递给后人的孟子的思想基本上是未经改动的。那本大部头的被称作《孟子》的书可能是他的弟子编纂而成,它比那些号称是最古老的文本更可靠。孟子在世时也曾经像孔子一样周游求仕, [68] 并且在某个时候还真的得到了官职。 [69]
如同孔子一般,孟子也相信“人民是国家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的福祉必须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孟子还(以几近乎与孔子相同的字眼)认为“政府的权力是从被管理者的赞成中得到的”。 [70] 孟子甚至主张,君主在签署死刑命令之前,应该得到人民的同意。 [71] 他宣称,政府应该交由有德有才的儒家学者去管理,而且,儒者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不应该受到国君的干预,因为国君从未学习过如何进行管理。 [72] 对于孔子倡导的特殊的经济措施,孟子也作了改进。在关于自然资源的对话中,孟子发表的言辞听起来是非常现代的。 [73] 然而,孟子也足够精明地坚持认为(像孔子和康德一样),单纯的谋利动机不能作为国家制定政策的基础。 [74]
孟子同意孔子的观点,即无能的君主没有资格享有王位。 [75] 但是,孟子比孔子走得更远,宣称如果一个君主停止了为人民造福,人民唯一的义务就是揭竿而起,并取而代之。 [76] 可是,君主的大臣则应该用纠正君主之错误的方式而防止这一切的发生。 [77]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孟子认为,学者的地位是最有价值的和最荣耀的。他对国君给予学者的礼物发出抱怨说,不是礼物不够,而是赠送的方式有问题,它迫使学者们不得不向君主表示感谢。 [78] 孟子说,即使是帝王也不应该擅自召唤一位杰出的学者去见他,而是应该去拜望学者,正如“古代有能有德的君王”所做的那样。 [79] 孟子认定的另一项原则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一旦确立,即使学生是君王,也应该把老师视为父亲或兄长,而不是看作他的臣下。 [80] 既然大多数学者是儒者,那么,王公贵族的大多数私人教师也一定会是儒者,所以,在儒学得到世俗权力的过程中,上述孟子的原则注定要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儒家学者,孟子不仅坚持了上述种种主张,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将这些主张付诸实施,因为他在几个国家的朝廷上很受欢迎。回味着他的有说服力的主张,会让我们认为儒学的盛行就在前面不远的拐角处。但是,孟子——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好的优秀儒者之一——也具有某些弱点,这些弱点在这个集群中的许多人中是有代表性的。
孟子其实是个附庸风雅之士。尽管他的日常生活和周游列国都很时新,但他还是深深地羡慕着那些生活更豪华的王公们。孟子深信,如果正义得以实现,他就会是帝王。 [81] 不过,既然做帝王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他就装模作样地轻视社会地位和奢侈生活,并表示自己不关心别的只关心道德。但是,就像某位淑女的表现一样,孟子矫饰得有些过火了。 [82] 在一些表述中,他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对世袭贵族的同情。孟子说:“管理政府并不难,只要不触犯世家大族的利益就行了。”在他看来,有了这些重要的贵族世家的赞同,一个人就可以“把他的道德学说传布到全天下”。 [83] 尽管孟子经常主张要根据德行授予官爵,但他也说:“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国君才应该提倡美德。因为,如果他一味地提倡美德,就会使社会地位低的人超过地位尊贵的人,而那些与王室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就会居于君王亲戚的上头,对此,做国君的能不慎重对待吗?” [84]
【按:这里贬低孟子的话,不知是原文还是翻译的锅,存在很大的问题。】
这种观点与孟子另外的一些表述是相当不一致的, [85] 当然也与孔子的思想有相当大的冲突。然而,这种类型的不一致遍及大量相对早期的儒家文献之中,因为儒生也是人。一方面,作为一个集群,他们参加了孔子发动的针对世袭贵族的斗争。但是,作为个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贵族家室的后裔,而且,只有依靠某些特殊贵族的恩惠,他们才能得到官职、要职,可能甚至是他们的衣食。这样一来,他们的忠诚和原则有时会变得模糊不清。
尽管会有这种模糊不清,孟子还是一位人类平等观念的坚定信仰者。 [86] 我们可以说,他可能试图证明他和君主具有一样良好的本性,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他并没有明确主张他自己生来就比别人更好。事实上,孟子相信人性本善,认为所有人的本性都是良好的。而且,古代的伟大圣贤也不过是普通人,所不同的是,这些圣贤完全发展了他们的固有本性。孟子对这一观点的论述很多, [87] 并且从心理学上讲,时至今日还使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们深感兴趣。他对这个论题的思索是独到的和透彻的,不过,这一观点的结局却并不十分幸运。
人性本善的学说可以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因为根据这种学说,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达到成功的顶峰。但另一方面它也会抑制创造性,因为,毕竟人们不用去做什么就获得了德行。孟子确实说过人们应该修养他们的品格,但他却并没有同样严格地坚持要求每个个人应该履行他们命中注定的义务,而《论语》却坚持了这一点。这可能是自然而然的。当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集群刚开始与世袭特权阶层展开斗争时,肯定要强调以下事实:出身贫贱的人与贵族具有相同的美德。但是,当意识形态的斗争开始取得胜利时,斗争的重点就转移到了所有人的平等,而个人的存在也就被淹没了。因此,虽然那些法国哲学家们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是个人主义者,但革命的口号讲的却是所有人的平等。
【按:这里的说法很值得商榷~】
具有孔子思想特色的斗争在孟子那里出现了松弛或缓和,这不仅体现在道德修养上,也体现在理性王国里。孟子认为,人性不仅是善的,而且也是一种缩影,即“万物完全就在人的自我之中”。 [88] 孟子以此推论出,依靠相对简单的反观自己内心的方法,人们就能获得宇宙万物的知识。 [89] 洛兰·克里尔指出,孟子之所以坚持这种观点,是因为他认为道德原则是宇宙中唯一值得关注的方面,而正因为有了这种信仰,与孔子相比,孟子才更少强调学习的必要性。 [90]
尽管哲学在当时的中国还很年轻,但有些人已经开始厌烦孔子的主张了。孔子的主张是,人们应该自己去寻求真理,并且不断地根据新的经验去纠正对真理的理解——这不仅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但是,那些厌烦孔子此种学说的人想要得到一种简易之法;当然,他们找到了它。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孔子和孟子所持的判断人的品格的方法。孔子说:
仔细审察一个人的奋斗目标,观察他的追求这些目标的方法,并观看能使他得到满足的东西。(这样一来,)一个人怎能掩藏住他的品格呢? [91]
但是,孟子拥有的是较为简约的方法,即:
孟子说:“在一个人的所有器官中,没有什么能比眼睛瞳孔更精良了。它不能隐匿邪恶。如果胸中一派正气,瞳孔就会闪闪发亮;否则,它就是暗淡无光的。倾听一个人的说话并观察他的瞳孔,一个人怎能掩蔽他的品格呢?” [92]
孟子的这个处方几乎具有魔法般的绝密效用。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特性一再出现在中国思想史中。
就学习意味着探索一种个人对真理的理解而言,简易之法的探求就意指更少的学习活动。这种简易之法,尽管相对来讲不太看重学习,但却并没有减弱而是加强了对于古人和被认为是经典的那些书本的重视。如果人们不愿意自己去寻求真理,那么,他就得拥有供他方便使用的现成的书本和传统说法。因此,孟子的一种说法极像墨子而非常不像孔子,那就是:“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个遵从先(圣)王之道的人却犯了错误。” [93] 那些想做完美的国君和大臣的人“只需要模仿尧和舜就够了”。 [94] 尧和舜的政治不仅是完美的,而且适合于所有的时代和地方,所以,孟子说,在国家税赋方面,要以尧和舜的标准为标准,任何程度的增加和减免都是犯了同样性质的错误。 [95] 尽管孟子没有像孔子那样很强调学习文献,但他还是从文献中引用了大量内容。 [96]
既然孟子的思想在许多方面相当不同于孔子,我们就可能要猜想,展现在《孟子》中的孔子会很不同于《论语》中的孔子。可是,就总体上来讲,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在《孟子》中看到的孔子更像是《论语》前15篇中的孔子而不是后5篇中的大部分章节所描绘的孔子形象,而这后5篇是后来编集而成的。 [97] 根据这种一致之处,我们完全可以说,《论语》和《孟子》中的有关孔子的记载是正确的。不过,正是因为这种记载太多了,才使得有关孔子的传统说法在后来发生了完全的改观。孟子深信,孔子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并觉得有必要解释为什么孔子未能成为帝王。 [98] 让孟子认识到以下实情是困难的,那就是:即使在一个具备了良好条件的时代,孔子也根本不会得到政治地位。而且,在他的时代,孔子确实从未得到过一个真正的有实权的官职。因此,尽管孟子反对给孔子编造的某些故事, [99] 但他还是认为,在大多数时候,甚至在周游列国期间,孔子也是有官职的。孟子还断定,孔子曾经是鲁国的司寇。 [100] 《孟子》中所记载的孔子担任司寇的这一章节,是认为孔子做过如此高官的最早记述。 [101]
即使孟子本人并未在很大程度上错误地传达孔子的思想,但《孟子》这本书却做了大量的这种错误传达。因为《孟子》是我们拥有的最早的明确讨论儒家哲学的著述,并且它比《论语》更容易理解,那么,一种相当自然的看法就是,那些《论语》中模糊不清的地方或孔子的学生们未加记述的地方,人们就可以(有时是无意识地)用《孟子》的记载加以补救。于是,孟子在某种场合下为世袭贵族所作的辩解, [102] 以及对封建制度表现出相当的兴趣等事实,就为那种认为孔子是封建主义卫士的观点提供了支持。既然孟子说过人们需要做的只是效仿古代圣王,就有人断定孔子也作过同样的告诫。
当孟子说“所有事物完全在一个人的自我之中(万物皆备于我)”时,他讲的是一种倾向于神秘主义的方法,或者至少是非常不同于孔子遵循的常识。孟子的以下两种说法走得更远。他先说:“大众一生追随着大道却没有理解它。” [103] 在描述圣王治下的人们的生活时,他又说:“他的人民有一种深为满意的态度。即使圣王杀死他们,他们也没有怨憎;当圣王做了对他们有利的事情时,他们也没有感觉到从中受益。他们每天都在向善进步,但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无论何处,只要是真君子经过,事物就有了变化。无论真君子住在哪里,他的影响都像是神灵的影响;上下飘荡,与天地合为一体。” [104] 这种说法与道家书籍中的某些章节极其相似。 [105] 如果《孟子》中的这些部分是真实可信的,那么,它就说明孟子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106] 总之,这种现象使人们充分认识到,道家思想很快就开始深刻地影响整个儒家思想了。
要对道家学说做出确当的叙说得写上好几本书,但我们在此需要的是一个简要的概括。众所周知,最重要的道家著作是《老子》和《庄子》。传统观点认为,《老子》(亦称作《道德经》)是由稍早于孔子的一位名叫老子的人写成的。最近的研究证据表明,老子可能是传说中的人物,并且称作《老子》的这部书的完成不会早于孟子时代前后,如果能有那么早的话。这后一种观点显然是正确的,并且在当今大抵已为多半学者所接受,尽管这个问题仍在争论之中。 [107] 一般认为庄子是大约与孟子同时代的人。《老子》和《庄子》不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一些学者认为,甚至晚到汉代,它们还被改变和增补过。它们并没有显示出共同的哲学思想,而实际上在这两本著作中还有许多内在的不一致之处。不过,它们也的确是呈现出了一种明显的道家思想类型。
道家思想基本上是对当时流行的种种思想形态的反动。统治者和他们的走狗有意尽其所能地奴役和剥削大多数人。儒者和墨者以他们不同的方式宣称,人的义务就是加入到为和平、正义和对人的仁慈而进行的斗争之中。道者则宣称:“这两家说的都是多余的!”作为个人,他们有权利过他们自己独立的生活。人们谈论人的义务,但谁知道它们是什么呢?人吃牛排,猫头鹰吃老鼠,哪个才是正当的呢? [108] 如果所有事物都是相对的,儒者谈论的仁慈和正义之类的东西又怎么能有其确定性呢?“从前,庄周(即庄子)梦见自己是个自得其乐地翩翩飞舞的蝴蝶。他不知道他是庄周。突然他醒来了,并再次成为他自己。但现在他却不知道他到底是以前庄周做梦中的蝴蝶,还是现在蝴蝶做梦中的庄周。” [109]
这基本上是一种神秘哲学。对孔子来讲,“道”是行为方式。但是,对道家来讲,“道”则是宇宙的基本原则和质料。它本是无形、无欲、无争的,是至高无上的满足和幸福。它存在于天和地之前。在各种事物和制度的发生过程中,人们逐步远离了他们的原初状态,而在原初状态中,人本来是无所谓善与乐的。因此,所有的人为之事都是坏的。所以说,只是在“道”停止了存在之后,德行才开始流行。 [110] 学习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可能使自己过度紧张。 [111] 无论如何,“聪明的人并不博学,博学的人并不聪明”。 [112] “一旦我们放弃了学习,就再也没有什么麻烦了。” [113] 作为人造机构的政府是一个错误。“小毛贼锒铛入狱,大贼寇却成了诸侯。” [114] 《老子》以非常相似于儒家的方式猛烈攻击暴虐的惩罚、过度的税赋和不断的战争。 [115] 道家的圣人看重知足,即使给他们以高官,甚至是王者之位,他们也会拒绝的。 [116]
道家思想追求中的这一方面几近乎纯粹的个人主义。“道的真正目标是节制个人的欲望。” [117] 当一位道者问庄子如何治理天下时,庄子回答说:“让你的心灵找到它对纯粹天真的享受,使自己混沌于宇宙的基始元素中,与万物成为一体,遵循事物的自然规律,不作自私的考虑。能做到这些,世界就会被治理得很好了。” [118]
因此,追求幽远的道家思想是具有挑战性的、卓越的和首尾一贯的。道家哲学的基本核心触及到了每个中国人的心灵,无论他属于什么思想学派和宗教派别。它使许多人产生了怀疑主义、高度的忍耐性以及不受外界环境影响的享受生活的能力。没有它,中国的绘画和诗歌将是非常不同的另外一种模样。总之,道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可是,道家思想另外的一个方面却产生了不那么令人乐观的结果,因为它认可了极权主义。尽管这可能被看作是对“纯粹”道家思想的背叛,但是,道家思想的这个方面却存在于甚至是最早的道家著述中。具体说来,根据道家的思想,既然道家的圣人认为他与宇宙整体是同一的,那么,侮辱、伤害甚至是死亡就都不能奈何他。因此,他是攻不破的,并且(要注意这样的变化)也就是压制不住的。既然他不能被抬升或降低,他就是所有生灵中的至高无上者。 [119] 因为他与道同在,所以就具有了道的属性,并且握有自然本身的强大力量。他像天和地一样不讲仁慈。不论他对百姓是仁爱的或是暴虐的,都会从根本上视他们为他的玩物。 [120] 事实上,道家的圣人起的是上帝的作用。
既然人们应该回归到原初自然质朴的状态,至少对某些道家人物来说,就很难抵制这种想法:他们应该强迫人们这样去做。因此,在道家人物可以“控制世界”以及他们应该如何管理世界、压制人民并使他们无欲的方法之中,人们就看到了相当令人惊讶的表述。《老子》告诉我们:“圣人治理世界的方法是,掏空人民的头脑,填饱他们的肚子,削弱他们的意志,强壮他们的筋骨,使他们一直保持在无知无欲的状态中。” [121] 在《庄子》中我们则读到,“法律就是严厉而苛刻的,并且一定是要公布出来的”。 [122] 这样的一些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哲学核心明显是相冲突的,并且它们代表的是对其思想核心的曲解和滥用,但是,它们却有着极大的影响。
《老子》从未点名道姓地提到过孔子或儒者,尽管它明确攻击了他们的哲学。 [123] 《庄子》认为儒学是它的首要敌人,并在其33篇中不下21次地论及孔子。在某些章节,《庄子》直接攻击孔子,指责他有不正当的品行,并对他加以嘲笑和辱骂。 [124] 可是,一般来讲它的做法是相当精巧的,并声称孔子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方法是错误的,于是就改信了道家思想。因此,孔子不断地被引述为用十足的道家方式在讲话,并取笑那些实践儒学的人。
在今天,尽管相对来讲没有多少学者相信这些故事,但过去却有许多人认为,由于老子的作用,孔子在其晚年改信了道家思想。但是,这些故事有许多漏洞。不能说《论语》全部出自(被认为是发生过的)孔子改信道家思想之前的时期,因为有证据表明,还有一些相反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论语》中的一些内容明显带有道家思想的痕迹。 [125] 不过,《论语》并没有指示出孔子的思想有过向道家思想的转变。 [126] 而且,《庄子》塞进孔子口中的言辞在孔子时代是不为人所知的。 [127] 最后,《庄子》本身在孔子改变思想之日期的问题上也是不一致的。孔子被说成是早在51岁时就通过老子而受到了道家思想的教诲,并在60岁时改变了思想。 [128] 然而,《庄子》的另一章却引述孔子的话说,他在65岁时还从未听到过道家学说;从时间上讲,他曾经再次改信了儒学。 [129] 不过,在这本书的另一部分里,孔子直到71岁时还是个死不改悔的儒者,这显然是不认为孔子是个道家人物。 [130]
在读了这些带有令人眩目的怪异之论和表现出严格犀利的批判精神的道家著作之后,没有一个现代人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毫无疑问,它们以其霹雳般的冲击力撞击了古代中国的思想界。很大一部分自称为儒者的人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根据《庄子》某些部分的记载,孔子自己不也是最终成为老子的弟子了吗?因此,我们在《论语》的后边部分(这是相对晚一些时候附加上去的)就发现了大量道家思想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了被认为是孔子本人所说的话语。 [131]
这仅仅是儒学受到一种思想类型全面渗透的一个方面,而此种思想类型,即使不全是道家的,也与道家思想有联系。儒者群体中的寻常之辈认为,孔子式的获得真理的方法——刻苦学习和有条理的思考——真是太费力气了,而《老子》却提供了一种较为简易的途径,那就是,如果一个人达到了道家圣人的智慧高度,他就会“不用出门而知道了整个世界,不看窗户外面就见到了天道。……所以,圣人不外出也知道,不看事物也能正确地称呼它们,不工作也有收获”。这对于某些人显然是最具吸引力的。 [132]
另一个获得知识的捷径也被找了出来,那就是大约在这个时代前后成熟起来的如下理论:万物都由阴和阳(消极的和积极的原则)组成,在此基础之上,复杂的自然现象也能非常容易地得到解释。 [133] 人们也开始迷上了数字,认为它们是打开宇宙奥秘之锁的一把简易的钥匙。 [134] 这些原理被运用在了对一本叫作《易经(变化之书)》的古代占卜手册的研究上了。这本书的原初部分(卦辞和爻辞)早于孔子时代,但现在却有了十个附加部分,叫作“十翼”(“翼”是翅膀、辅助之意)。它们来自各个时期,但所有的都比孔子要晚,其中某些部分可能不会早于汉代。 [135]
为了使“十翼”具有权威性,它们被说成是由孔子编撰的。其实,它们只有7篇而不是10篇,其中头3篇中的每一篇都被分成两部分。它们显然有不同的作者,所以应该个别地加以看待,但这会过度延长我们的讨论。总的来说,它们是对《易经》原初部分之思想的评论和引申;它们比原初部分更易于看懂,也更有哲学味。“十翼”的第三和第四个部分(《系辞》上、下)经常有“夫子说(子曰)”这样的字眼,这明显是指孔子。 [136] 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孔子不是它们的作者。
“十翼”中的常用词几乎是孔子从未讲过的,同时,这些词汇并没有出现在与孔子时代一样早的任何古代文献中,也没有出现在《论语》以及甚至晚到像《孟子》这样的著作中。这个结论也适合于二元论的概念“阴”和“阳”,它们出现在整个“十翼”中,除了最后两部分(《序卦》、《杂卦》)。同样,“地”的概念,作为在形而上学的天地二元论中的“天”的对应部分,是在前儒家的文献中看不到的,并且没有出现在《论语》中,但它却作为一个明确的形而上学词汇出现在除最后两篇的所有“十翼”之中。 [137] 这些后来的词汇没有出现在“十翼”的最后两篇之中,这无疑是意味深长的,但对我们现在的研究却没有什么重要意义。这两篇论文极其简约,并且绝对肤浅,根本没有理由认为孔子会劳心费神地去阅读它们,更别说去写作这种琐屑的东西了。
“十翼”的大部分其他篇章也是很浅薄的。其中的很多内容是荒谬的,而其不太荒谬的篇章中的大部分也是绝对陈腐和平庸的。这样的作品使人想起当今出版的那些手相学、骨相学和超科学之类的手册。他们的作者,词汇丰富而思想贫乏,企图使用令人印象深刻的词汇来掩盖这样的事实: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东西。
孔子没有撰写“十翼”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如下事实:弥漫在它们之中的哲学不仅不存在于《论语》之中,而且与《论语》中的哲学完全相反。《论语》说孔子不讲“怪异现象”或神灵。然而,“十翼”的第四篇(《象》下)却说:“夫子说:‘……云跟从着龙,风则跟从着虎。(云从龙,风从虎)’”而且,从总体上讲,“十翼”充满了神奇的和形而上学的语言。孔子认为,知识是一种通过经验和思索而艰难得到的东西,但《易经》却提供了一种相当简易的方法。人们只需要学习这本书,学习它那神秘的数字科学(“与万物对应一致的数字是11,520”)和它的六条线的卦象,就可以极其有效地“知道所有事物”。 [138]
如果孔子认为有如此简便而有特效的方法能够解决所有的疑虑,那么,对于这样的事实,他就应该在《论语》中做出某种程度的提及。然而,除了《论语·述而第七》“加我数年”章(这一章无疑是后来插入的)外, [139] 根本就没有提到过这回事。而且,没有任何一种早期资料说过孔子曾以任何方式进行过占卜。有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占卜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普通的做法。在孔子时代之前好久,殷商一朝,人们就不断地寻求占卜的指导,到了周朝早期,这种做法仍在继续。 [140] 《左传》和《春秋》的记载证明,就在孔子在世时,并且就是在他的家乡鲁国,占卜也是习以为常的,个人和政府都使用它。 [141] 《易经》也告诉我们,君子在行动之前总是要问卜的。 [142] 然而,就我们知道的而言,孔子从未求助于占卜。孟子显然也是如此。
事实上,《易经》“十翼”大部分篇章中的占卜哲学和世界观与孔子思想以及与即使是最早的儒家思想都是不相干的。一些中国的、日本的和西方国家的学者都同意这个结论。 [143] 在《论语》的一章中,孔子提到了占卜,但他批评了这种做法。 [144] 正如傅斯年指出的:“孟子没有说过有关《易经》的一个字,而荀子则是顺便提到过它。……他谴责了占卜的做法。” [145] 当荀子列举儒者应学之书时,并没有提到《易经》。 [146]
可是,没有理由要求儒家学说应该只由孔子和几位大儒去创造。吉本很恰当地评论道:“一种怀疑主义的和保留意见的状态可以使一些具有探索性的心灵感到欣喜。但是,对大众来说,迷信活动是那样地投其所好,以至于如果他们被强制性地从美梦中唤醒,就会痛惜失去了使他们感到愉悦的美好幻景。” [147] 在古代中国和古罗马,就有人采取步骤去恢复此类迷信做法。有大量儒生向往道家思想,需要打卦问卜,所以,他们就需要孔子认可这些东西。在“十翼”中,他们得到了所有这三者。
“十翼”无疑是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大杂烩。 [148] 它的一些篇章反复引用孔子的话,视他为最令人尊敬的“夫子”。因此,孔子被用来称颂《易经》的完美,并把它推荐给所有人。 [149] 在“十翼”所引用的孔子的话语中,完全承认了《易经》的寻求真理的简易之途,并且孔子还问道:“有什么必要去思索?有什么必要而焦虑?” [150] 这些话还一字不变地出现在道家著作《庄子》之中, [151] 所以,这些话显然是从《庄子》这本书取出,并被“十翼”塞进了孔子口中。可是,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我们有出自《论语》的孔子更早的观点。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就会有近在手边的麻烦。” [152] 《庄子》引述了孔子的这句话,并把它扩展成一段伪造的文字,说孔子曾经研究过八卦和阴阳。 [153] 到了汉代,孔子被宣布为“十翼”的作者。尽管这个观点一再受到怀疑,但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学者仍然认为孔子撰写了其中的某些或全部篇章。
然而,有一个事情被遗漏了,那就是《论语》并没有提到过《易》。不过,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一些学者认为《论语·述而第七》“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中的“易”字是被作了改动,以使它显得像是指的《易经》罢了。另一些学者则直接认为,这一章是附加进去的。 [154] 《述而第七》“子疾病,子路请祷”章也被改变得像是指占卜,但对这一章的改头换面的说法只出现在一部道家著作中,在《论语》中却并没有发现一处地方传达出了这样的内容。 [155] 另一些可能是附加在《论语》中的章节仍然处在这种相同的影响之下。《子罕第九》引述孔子的话说:“凤凰不来了,河里也不再呈现图画了。我算是完了!” [156] 凤凰是一种预示好兆的鸟,河图是一种算命卖卜的图案。孔子在其他地方从未提到过这些内容。顾颉刚指出,这一章等于是说《论语》中的孔子是相信超自然的;顾氏直截了当地指出,它“暴露出了重大的嫌疑”。 [157]
中国思想界的新思潮使人们对于孔子的看法产生了很大变化。这可以从几本书中寻得线索。
《左传》已被多次提及。要想了解周朝的历史,这本书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资料来源,不过,它是一座信息与讹误兼而有之的金矿。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以许多不同的标准为基础,它的编纂日期是在西元前300年左右。 [158] 一般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是对《春秋经》的注释,但有许多学者指出,《左传》的很多地方与《春秋经》的记载根本没有关系。所以,《左传》更可能是一部合成之书,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古老的文献。不过,它显然并不仅仅是由一些五花八门的材料拼凑而成的。相反,常镜海的观点是很正确的,他说:“《左传》具有一种突出的动机。……其中的事实都是被筛选过的,以便说明历史学家个人的信念……” [159] 从总体上讲,它体现的是儒家的观点,尽管还散落着一些与儒家观点相反的章节,但在这样的一部巨著中,这种不同并不突出。
显而易见的是,《左传》的作者或作者们一方面是以真实的历史文献作依据来编写这本书,而另一方面又毫不犹豫地对这些材料加以润色,以便证明他们的观点。我们很难以任何其他理由说明《左传》所具备的首尾一致的特点,这一特点体现在一次又一次的预告未来上,而这种预告,通常都具有毫厘不爽的准确性。 [160] 马伯乐指出,西元前629年该书做出的一个预言说,在300年后将要发生一件事,而事实上刚好发生在西元前320年, [161] 这显然是《左传》的编纂者们在西元前300年左右把这样的预言性的材料加入到了书中。这本书也经常使用那个时期(西元前300年左右)的语言,其中充满了诸如此类的现象:超自然的预言、龙、邪恶的鬼怪、六天后复活的尸体、会讲话的石头,以及其他等。 [162] 它经常提到用《易经》来占卜(有着不可思议的应验),还多次引证“阴阳”和“五行”(通常被译作“五种元素”)的概念,而事实上在《左传》所记载的那些事件发生的时代(西元前722—前466年间),这些概念还不为当时的人们所知晓。 [163] 这个事实甚至使现代的一些颇具鉴赏力的学者产生误解,认为这些概念早就存在了,因为它们在《左传》的对话中被提到了,而《左传》又被看作是写成于东周早期的文献。
不过,有大量证据表明,《左传》中的许多对话是虚构的。人们已经确定了的产生于那个时代的其他著作都具有《论语》那样的语言简洁的特点,但《左传》所使用的却是冗长而不乏细节描写的语言,即使是密谋之会也不例外,并且暴露出人们内心的赤裸裸的动机。这是一部具有杰出创造性的作品,但是,作为历史记载,《左传》只能与莎士比亚的《朱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而不能与凯撒的《高卢战记》(Gallic War)相提并论。然而,它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作也不尽相同,因为《左传》的首要动机既非艺术又非历史,而是政治宣传。因此,每个长篇讲话都是偷偷地塞进一些儒家教条。结果是,这种夹带在有些时候就显得很不适当。据此书记载,鲁国的一位高级官员作了一次冗长而高调的讲演,说的是不能宽恕弑君之罪。可是,他在另一场合曾公开承认他自己曾犯过这种重罪。而且,在这番高谈阔论(被认为是作于西元前609年)中,这位官员不断提及尧、舜和其他一些人物,但这些人物都是在后来的传说中才出现的。因此,我们一定得以极大的疑虑看待诸如此类的谈说。 [164]
“蛮夷”之邦的楚庄王(西元前613—前591年在位)是一个淫逸、暴虐和好战的君主。当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位大臣杀死了它的完全沉湎于酒色之中的君主时,楚庄王便进攻了这个国家,占领了它的领土,还车裂了这位大臣。 [165] 这位大臣的母亲是一位有名的美人,楚庄王就想把她带到他的后宫中去。但是,当有人劝告他这样做很失策时,他就把这位美女赐给了他的一个属下。楚庄王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直到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166] 然而,《左传》却记载了这位武夫的几次讲话,那被认为是在他在位的中期所讲的。在这些讲话中,楚庄王使用了相当儒家的词汇,详谈了人性和善良信仰的必要,谴责了战争,并自责为残忍的侵略者。 [167]
《左传》的作者或作者们显然不认为他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妥。相反,在他们所认定的任何合适的地方,他们都会有意识地把那些琐碎的、令人厌烦的儒家说教加入到了行文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并未改变他们所掌握的历史事实,这说明他们还是有良心的史学家。至少,他们没有把这些事实改动得太厉害,以便使他们为他们笔下的人物所写的讲话看上去完全有道理。当然,在这些插入的想象性讲话中,也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麦考利(Macaulay,1800—1859,英国史学家)写道:“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和奎恰迪尼(Guicciardini,1483—1540,意大利史学家)模仿李维(Titus Livius,西元前59—西元17年,罗马历史学家)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古希腊历史学家),为他们的历史人物撰写了讲话。”而他担心的是,这种做法仍旧(在1828年)被某些欧洲作者所遵从。 [168]
当然,我们并未奢求《左传》中的儒学观点会与孔子的学说相一致,或者它所描绘的孔子完全是符合历史真相的。很自然的,这本书中的孔子不仅可以预言未来、显示出超自然的知识,而且还跟一个精通龙的知识和其他玄妙学问的人学习过。 [169] 根据《左传》的记载,孔子的家世是那样地有迹可查,以至于使孔子成了商朝天子的后代和宋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这样的说法丝毫不会令人吃惊。 [170] 《左传》还引用孔子的话来责骂那些对当权者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的人,说他们是轻举妄动的。对于这样的记载,其实我们也不必过分惊讶。 [171] 它们充分说明,到了《左传》成书的年代,在那些自称为儒者的人们当中确实出现了许多“明智”的人,他们深知,审慎好过勇猛。
使人惊诧的事实是,这本历史书尽管在时间上涵盖了孔子一生,并且是在儒者的主持下有意图地写成的,但在实际上却与孔子的生平没有什么正面的关系。其中没有孔子传记,甚至没有与传记写作有关的材料。 [172] 《左传》中与孔子有关的记载只是非常少的一些零散事件,并且其中的某些事件很显然不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其中的一例是认为孔子长期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并且还记载了一则轶话,而这则轶话是很荒谬的,以至于18世纪(在朝廷主持下)组成的一个校订《左传》的中国学者委员会把它删掉了;这些学者还引述了许多以前的批评家们的观点,认为这样的轶话是“俗儒”的伪造。 [173]
《春秋经》的另两种早期注释叫作《公羊传》和《穀梁传》,尽管它们都是儒书,但对孔子的生平却几乎没说什么。但奇怪的是《国语》中的情形。高本汉认为这部书大约写成于《左传》成书的时代。 [174] 在有关鲁国历史方面,《国语》共有两部分。我们确实希望在这本书中找到孔子的生平事迹,但却根本没有这样的记载。它仅仅提到了一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孔子是被当作一位智者而接受咨询,通常被问到的又是些超自然的东西,而孔子所做的答复经常提到神灵和预兆。 [175] 但是,在这部书的记载中,孔子没有得到什么职务。以上分析说明,在孔子去世后200年左右的时候,他的生平事实已经鲜为人知,后来逐渐出现的填补这些空白的传奇的丰富发展在此时还只是个开端。
对于孔子生平记载甚少的情形并没有保持多久。生动的想象很快便弥补了无论什么样的历史空白。有关孔子生平的产品获得了大丰收,并被汇集在一部叫作《孔子家语》的书中。对于这本书的成书时期,学者们是有争议的。韦利认为它“代表了西元前3世纪儒家传奇的发展”,其他学者一致认为它是西元3世纪的伪书。 [176] 毫无疑问,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书与古代也叫这个书名的那部书是不一样的,但也有人认为,那本叫作《孔子家语》的古书仅仅是被部分地作了改变或增补,最终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希望从这本书中找到有关孔子的确凿信息。即使其中的某些事件是真实的(而有一些可能是真的),也已经与不可靠的荒唐事情混杂在了一起,使它在整体上难以让人相信。在这本书中,孔子反复识别预兆并预言未来。事实上,它还引述一位孔子弟子的话说,“夫子无所不知”。 [177]
像这样的书,以及其他晚出的和虚构的关于孔子的故事和传说,与《论语》相比,在描绘为人们所能接受的总体上的孔子形象方面更有影响力。这样的结果是很令人痛惜的。不过,我们已经看到了荀子的抱怨。荀子认为,在他的时代,太多的儒生是贵族的食客和走狗,《孔子家语》恰当地反映了他们的谄上傲下,并借孔子之口肯定了严重的阶级差别。 [178] 孔子还被描绘成这样的一个人物:策划大规模的阴谋,使东部的大部分地区陷入血腥的战争之中,以避免鲁国受到单独的进攻。 [179] 这是已经被证明了的历史时代上的错误。它也使孔子赞成“欺骗野蛮人”,并建议对一些罪行,包括“发明奇怪的衣服”处以死刑。在这两个方面,它与《论语》的记载截然相反。 [180] 诸如此类的情形还有很多,但是,若要一一列举它们,将是件单调乏味的事情。
在《孔子家语》的伪造部分中,我们很难确定它们到底对孔子有多大程度的心存恶意。可是,这部书无疑是在强烈的道家影响下写成的。《孔子家语》说孔子整理了占卜之书并用《易经》问卦。 [181] 它至少有一次把《老子》中的语句塞入孔子口中。 [182] 《孔子家语》还说孔子找到了老子以便跟他学习,这与某些别的晚出之书之所为如出一辙。它让孔子甚至在见到老子之前就称他为“我的老师(吾师)”,还认为孔子只是在受到道家圣人的启迪之后,才开始获得巨大名望。 [183] 在仔细核实了那个关于孔子和老子之间进行对话的故事之后,人们只能同意沙畹的看法,他认为,这种故事是“道家人物的发明。……他们进行了最自由的想象,并且大言不惭地肯定了它的准确性……” [184]
还有一些书讲到了孔子的祖先,这些书(尽管其中的一些伪称很古老)经过批判性的研究之后,成书日期被定在了西元前3世纪或更晚的一些时候。我们不可能弄清所有的这些故事。总而言之,《孔子家语》讲述的有关内容与这些书中所说的孔子祖先的大部分情形都是一致的。无论如何,要寻求了解真孔子的人们是不能没有任何保证地去使用它们的。
最后一位早期硕儒是荀子。他的生卒日期无法确定,但他显然是生活在西元前3世纪的整个前50年当中。 [185] 荀子出生在北方的赵国。他旅行到了齐国,并在那里得到了一个官职。后来,他到了南方大国楚国,并且也曾任职。另外,他访问过秦国。所以,荀子的经历很可能比孔子和孟子更广泛、更多样。这个事实反映在了他的思想中。
荀子是世界性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他的大部分思想是那种令人钦佩的、我们喜欢用我们俗气的乡土观念称作“现代”的那种东西。仅是他的《正名》篇就有比某些哲学家的全部作品具有更透彻的分析和更深邃的智慧。 [186] 他的很多思想是儒学高度理性的传统向着新的明晰阶段的逻辑发展。尽管(其原因我们马上就会考虑)他在后儒中不太被欣赏,但是,后世儒学中的大部分精彩篇章都留下了荀子思想的清晰印记。他极大地发展了“礼”在教育中所起作用的理论,而这一理论,在孔子那里仅仅是提了出来。事实上,具有很大影响的经典——《礼记》——中的一大部分一字不变地抄自那本叫作《荀子》的书。荀子率直地谴责他那个时代光芒四射的迷信思想。他把天解释为自然秩序,并宣称,与其害怕预兆和鬼怪,还不如害怕腐败的政府和混乱无序的政治。有人问他为什么祈雨之后就下了雨,他回答说,无论祈雨者是否祈求,天都会下雨的。 [187]
在某些方面,荀子的思想标志着早期儒学的高峰。但是,中国人有句格言说,最伟大的成功时刻也是衰败开始的时刻(“盛极必衰”)。在某些方面,荀子毋庸置疑地扭转了孔子所开创的儒学的发展方向。其基本的原因是,荀子对人性缺乏信心。孔子思想的基础是相信协作社会的可能性,在此社会中,人们将彼此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地在一起工作,也就是说,组成社会的人们不仅仅像群聚的羊那样需要被驱使,而且应该在选择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时候发挥一定的作用。可是,荀子认为,人们必须被严格地指挥着进入他们应走的道路中去。
孟子在他的几乎是出于情感上的对人性本善的坚持中,已经超越了孔子说过的任何东西。可能是因为荀子具有不同文化环境的较广泛的经验,以至于坚持认为不能依赖人性使人成为善人。荀子看到,同一种人在不同的环境中会逐渐变得非常不同,为此,他强调了后天训练的突出作用。 [188] 他还宣称,“人性是恶的,他的善性只是后天接受训练的结果”。 [189] 我们见到过墨子传布极权主义。荀子的思想则是,除非经过适宜的训练,否则人们将永远会被“自私、不道德和不公正”所促动,顺着这样的方向一直走下去。 [190]
如果人本来就是恶的,就得有某种外来的东西加诸人身,使人变善。荀子告诉我们:“所以,先前的(圣)王为人们发明了礼和义。” [191] 在荀子看来,智慧和道德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真理,人们可以学习它,但却不能给它添加什么。实际上,没有合格的教师,人们甚至都不能学习它;而对于这样的教师,人们必定是从不敢表示异议。“一个人不认为他的教师所拟定的规则是正确的,而偏爱他自己的方法,这好比是让盲人辨别颜色,让聋子辨别声音;他不可避免地要走上混乱和错误之途。” [192]
一个人逃脱他的天生邪恶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所以,荀子着重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但在荀子看来,学习,并不是如孔子所主张的,是一个“听到和看到更多东西(多闻多见)”,进而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智力进行理解的进程。 [193] 而在荀子这里,必须把学习限定在明确划定的论题之内。在此,荀子可能受到了道家学说的影响。可是,荀子并没有像许多儒生那样被道家学说弄得昏头昏脑。他率直地反对道家思想中粗俗的迷信观念和神秘主义,还点名批评了老子和庄子。 [194] 不过,道家思想在他的时代是那样地盛行,以至于他很难避免受其影响。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孔子是一位极其严厉的学生的监工,他要求学生们不懈地探求真理。道家人物嘲笑这一点,宣称这种努力是无益的和危险的。道家的这种立场是要求顺应人的自然欲望,而不能说是懒惰的表现。《庄子》说:“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知识是无限的。用有限去寻求无限,的确是危险的。” [195] 荀子用不同的字眼明确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196] 因此,荀子责难所有的学习和研究,除非这样的学习和研究不超出他所划定的范围,因为他认为他所规定的范围才符合真正的思想传统, [197] 他甚至还特地为此开列了一个学习经典著作的清单。他说,学习“开始于诵读经典,结束于学习礼”。 [198] 正如德效骞所说:“荀子把儒学发展成为一个权威主义体系,在其中,所有真理都来自圣人的说教。” [199]
这种权威主义并未止步于知识领域。既然荀子认为过去的圣王创制了约束人民的礼和义,那么,有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思想发展就是,荀子对某些所谓的异端思想感到痛惜,并宣称当今明智的国君应该“以独裁对待人民,用大道指导他们。……并用刑罚去约束他们”。 [200] 冯友兰认为,荀子的这种思想之所以应该受到指责,部分地是因为,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在稍后不久便处在了法家极权主义的控制之下了。 [201]
因为孟子讲了所有的人一样地性本善,荀子就反过来说人性本恶。根据双方的观点,所有的人都处在同一水平上。但荀子比孟子走得更远,坚持认为人应该根据才能而不是世袭特权而获得社会地位。 [202] 然而,无论其根据是什么,荀子强烈地相信阶级的区分,还宣称这对于良好秩序来说是必要的。与孔子想望的“富民”不同,荀子主张,为了各阶层的利益,应该由圣王把人们分成“穷人和富人,贵族和平民”。 [203] 那些处在贵族阶层的人将“受到礼和乐的节制”,而普通人则应该受到严刑峻法的控制。 [204] 在此,荀子又一次与孔子分道扬镳,并预示了将在以后出现的那些有才能的新儒家贵族的特权。
《荀子》这本书所提及的孔子的大部分言论与《论语》中的孔子的言语相比是极其不同的。这部书自然也出现了一些故事。它们不仅说孔子是鲁国的司寇,还说孔子因此就使人民的面貌焕然一新。 [205] 然而,这部书总的来说并没有多少不可思议和不能令人相信的内容。可是,《荀子》的最后六篇就不那么可靠了。其中包含了一些怪异的轶闻,并把孔子提拔到了鲁国“代理宰相”的位置上。可是,这些篇章无疑是后来加入到书中的。 [206]
第十三章 灾难
在孔子时代之前后,古代中国政治分权化的进程已经臻至顶点。天下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混乱局面,使人们普遍认识到了进行补救和纠正的必要性,而事实上,就有许多人试图利用不同的方法从事重新统一中国的事业。孔子希望出现一个由受过教育启蒙的人们志愿组成的联盟。他的理想酷似现代民主的理想,但是,因为教育还不普及,而且他在当时也设计不出把民主政治付诸实施的机制,所以,这个希望也就未能实现。而墨子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甚至更无济于事。
可是,有另外一些人提出了更为实际一些的计划,他们就是著名的法家人物。之所以称之为法家,是因为他们强调了法律在治世中的作用。不过,更能说明问题的称呼可能是把他们称为极权主义者,因为他们倡导最强有力的集权管理,并希望使个人完全从属于国家。
被称作法家的思想家们实际上并未组成一个学派,相反,他们也相互批评,在一次有名的场合,他们甚至相互消灭。 [207] 某些被认为是法家的书籍在成书日期和作者归属上都是可疑的,并且内容也很驳杂,以至于在这些著作的不同部分中包含有各种各样的观点(甚至有儒家的)。从这些书中挑选出各种材料,就可能得到不同的法家思想。在此,我们首要关注的是这样一种法家思想,它在西元前3世纪逐渐体现在秦帝国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它的这个意识形态背景,我们将把以法家哲学家韩非子名字命名的那部书的真实部分(就它们能被确定的而言)作为我们主要的材料依据。 [208] 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帝国的建立者及其主要法家谋士都深受韩非子思想的影响。
法家思想确实有一些基本的主旨和动机。法家思想家们声称,他们为产生一种有益于人民的政治秩序和一个有纪律的社会而忧心忡忡。在某些情形下,他们的此类动机无疑是相当真诚的。在位的君主被以下事实所吸引:法家思想给他们提供了进行绝对的专制控制的理由和方法。在法家思想中,道家的思想因素占有突出的地位。可能是法家人物中最伟大的思想家韩非子就经常引述老子的话,而《史记》则认为,韩非子的思想是立足于道家思想的。 [209] 道家和法家思想都是儒学的大敌。我们已经看到,尽管道家思想从逻辑上讲应该拥护无政府主义,但事实上它却在放纵统治者。根据道家思想,只要君主是个道家式的圣人,就可以发挥肆无忌惮的暴君式的耶和华的作用。道家思想中的一些狂热而神秘的文词暗含的正是这种极权主义倾向(这也可以在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地方见到)。法家人物在道家的此类主张中找到了那种他们翘首以待的语言。在后来中国人的“皇帝”的概念中,就认为皇帝是握有令人敬畏的权力的神秘圣人,并占据着“龙”位等,这些观念并非来源于儒学,而是来自经由法家传递的道家思想。
进而言之,道家和法家思想的联姻与人们长期以来寻求以简易之道行事的倾向是一致的。法家思想在许多方面是极其讲求实际和现实主义的,但法家人物并不是不喜欢把他们的原则呈现为形而上学的权威并使它们具有近乎魔力般的效应。中国历史上最堪称为法家人物的秦始皇,就埋头于道家的迷信和魔法之中。 [210] 这种人不可能不被法家的主张所吸引,因为法家宣称,君主一旦使用了他们的方法,就可以“躺在床上,听着丝竹之乐,而帝国却治理得很好”。 [211]
人们普遍认为,西元前3世纪的儒家是有着复兴古道之愿望的思想派别,而儒家之中的一些人甚至自己也这样认为。相反,自称为果敢的创制者的法家却具有新时代的新措施。 [212] 这种观点部分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因为法家的许多措施的确是新颖的。它们的某些经济政策,诸如允许买卖土地等,倾向于给予平民个人较大的行动自由。 [213] 不过,关于平民个人总体上的自由,法家的态度明显是反动保守的。正是儒者才是个人新自由的卫士,而这种自由在封建主义臻至顶峰时根本不为人们所知晓。另一方面,法家则认为,儒家倡导的这种自由是具有政治颠覆性的。韩非子非常清楚地表示,他反对持有这种自由观的学者。韩非子特别提到了儒者,他认为,儒者“通过修养仁义而得到信任,并得到了政治地位;他们通过修养文学知识而成为著名的教师,因为具有威望而受到提拔;可这些都是普通人的成就。但结果却是,他们没有任何实在的长处却得到了官职,没有贵族爵位却得到了提拔;政府遵循这种政策治国的时候,国家一定会陷入混乱,而国君也就处在危险之中了”。 [214]
法家希望取消西周建立的封建制,因为在这种封建制下不可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不过,法家人物为君主们寻求的这种极权主义者的权力事实上最近似于封建诸侯使用在他们的无依无靠的和愚昧无知的农奴头上的权力。因此,像道家人物一样,法家人物也希望“削弱人民”,并使他们保持在一种简朴的愚昧无知的状态中。 [215] 从这一点上来看,当《老子》讲“人民难于治理的原因是他们知道得太多”时,它的判断是实事求是的。 [216]
但是,对于当时的思想启蒙(道家和法家将此相当正确地归罪于儒者)的毒害却使得中国较文明的地区被完全彻底地摧毁了。然而,尽管法家竭尽全力,日历并不能永远地倒着翻下去。约略地看一下历史就可发现,极权主义很难有真正的光芒四射,除非人民会长期地对无情的纪律和暴虐的统治俯首贴耳。所以,法家思想未能在中国最有文化素养的地区(这里已有了新自由思想的发展)兴盛起来,这并非出自偶然。三位最著名的法家人物中,韩非子的出生地虽然是中原地区的韩国,但韩国却位于孔子学说的作用范围以外的西方,而商鞅的许多思想据说也是得自于这样的中原国家。 [217] 第三位法家人物李斯的出生地则是在部分地仍处于野蛮状态的楚国。但是,只有在边远的西部国家秦国,他们的学说才完全被赏识和实施。
有许多证据表明,正如戴闻达(Duyvendak)所认为的,秦国在文化方面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大部分地方原本都是‘野蛮人’”。 [218] 不过,正是与这些邻近的野蛮部落的不断战斗,才使得秦国的人民好战尚武,也没有闲暇进行文化活动。就个人而言,这个国家的人们都能够严守纪律并服从权威。当儒家哲学家荀子访问秦国时,就怀着极大的钦佩之心指出,这里的每个人都严格从事于国家规定的职业,也“没有个人的兴趣和愿望”。他的话听起来好像是在描述一个蚂蚁窝。他还非常喜欢以下事实:人民“非常惧怕政府官员,完全俯首听命”(对于这种状况,孔子定会有不同的评价)。不过,荀子在这里也发现了他认为的唯一的不足之处,那就是:秦国没有多少儒生。 [219] 像许多现代人一样,荀子既喜欢民主政治的自由,又喜欢极权主义的所谓效力,并认为没有理由去问为什么二者兼得是不可能的。
【按:说荀子喜欢秦国的统治倒也不算是,只是他身在秦国,不能全程说秦国的坏话吧!】
秦国被认为是从商鞅(变法)的时代开始走上繁荣之路的。商鞅是卫国统治家族的后裔。几个东方国家都不曾赏识商鞅的才能,他就在大约西元前4世纪中叶到了秦国,并在这里最终得到了荣耀和权力。作为高级大臣(大良造),据说他改革了政府体制,压制了贵族势力,创建了一个强大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他还推行了经济改革,打破了宗法家族的统一体,并利用奖赏举报者的方法使人民彼此对立。根据传统的看法,他利用种种方法使秦国发展壮大,以便与中原各国进行战斗。作为军队主帅,他还依靠作战谋略和背弃诺言而扩大了秦国的版图。 [220]
大约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持续竞争,在秦国逐渐扩大其领土的时候,其他国家则在同灭亡进行斗争。有时,这些国家也会联合起来对付秦国,但从未持之以恒,也没有产生过像样的效力。秦国军队的英勇(可能胜过作战方法)是重要的。但这个国家并非单只依赖战场上的较量。秦国也把秘探派往各国去赢得结盟,并用行贿以及必要时用暗杀的方法在东方各国之间挑拨离间。 [221]
荀子的两位学生对于秦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位儒家学者谴责秦国的征战, [222] 并对于法家思想的许多方面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荀子(无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孔子倡导的协作社会的理想,转而赞同极权控制。另外,荀子的人性本恶的思想暗示出,他的思想的发展结果之一很可能就是法家思想。因此,他的杰出学生韩非子就成为最伟大的法家哲学家,这是丝毫不会令人奇怪的。
韩非子是韩国公室的后裔,韩国则是秦国的邻国和主要敌人。据说,因为说话口吃,韩非子就专注于著书立说。现存《韩非子》这部书确有被后人增补和插入的内容,但也能从中区分出来韩非子的手笔。它们以无情的明确性和严格的逻辑建立了一个绝对极权的专制政治体系。韩非子认识到,只有强权才是至高无上的,而他的目标就是造就富裕而有权力的统治者。人民将完全被用作实现君主之图谋的工具,生和死都要适应君主的目的。对于一个君主来说,无论是表现出仁慈还是暴虐,都同样地有害、同样地无关紧要,因为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控制其权力。穷人不应该得到帮助,因为这只能使他们更穷,而人民的良好意愿是不名一文的。君主必须自己紧握所有的权力。他必须根据才干选择大臣,并且要用财富和社会地位而不要用权力和影响力奖赏他们。大臣不需要有德行,德行之人是罕见的。大臣也不应该是精明的,精明之人将欺骗君主。他们不应该太单纯,单纯之人要被人民欺骗。君主只要能把大臣和全部臣民保持在一种战战兢兢的状态之中,他们就不会胆敢犯错误了。总之,君主必须迫使每个人只为国家而生存。个人的思想和感情都是被禁止的。“所有与法律和规定不一致的言行都将被禁绝”。 [223]
与韩非子相比,马基雅维里在《君王论》中提出的策略便显得有些缩手缩脚和踌躇不决了。据记载,当时的秦国国君(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读了韩非子的两篇文章之后非常兴奋,并公开说想见到他。不久之后,韩国派遣韩非子出使秦国,韩非子因此会见了这位秦国国君,但另一位法家人物却先他来到。
这位先到者就是李斯,他早先也是荀子的学生。李斯远不如韩非子有才气,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李斯的长处是,他在秦国已经待了一段时间,并取得了秦国国君的信任。他最终设法害死了韩非子。 [224] 从此以后,大抵主要是靠着他的被谋杀了的同门和同事的思想的指导,李斯把秦国引向了胜利。
秦国的崛起和胜利是血迹斑斑的。据记载,有一次,被秦军包围的40万士兵全部被屠杀。 [225] 这个数字无疑有些夸张,但却是可作参考的。到了西元前221年,秦国吞灭了全部中原国家。 [226] 法家人物所主宰的极权者的国家变得至高无上了。
效率是那个时代的准则。“法律和习俗取得了一致,度量衡被标准化,车轮之间要有同样距离的间隔。 [227] 汉字书写形式整齐划一” [228] 。根据同样意义深远的精神,秦国统治者采用了“始皇”的称号,并暗示着说(既然这个朝代永远不会再次发生变化)他的王位继承人(从“二世”开始)仅仅从数字上讲就将“达到千万以至于无穷”。 [229] 这种说法给人的印象是,秦朝的统治者实在是过分妄自尊大了。我们已经指出,这位始皇帝是非常迷信的。西元前219年,他因为对一座山发怒,就派了3000名囚犯去砍伐山上的树木。 [230] 对此我们可能感到好笑,但当全体人民都是他怒火中烧或奇思怪想的对象的话,这种结果就不太幽默了。根据法家的原则,轻微的违法行为就要受到酷烈的惩罚。许多人被流放到边远地区,就像典当物一样。秦始皇使用囚犯和强迫征用的劳力修建了许多宫殿和耗资巨大的公共工程。仅在首都附近据说他就有270处宫殿,里面满是美女和精致的器物。 [231] 在他的陵寝工地据说有70万人在劳动,长城的建造更是消耗了大量的生命。为了从资金上支持这些项目,必然得对人民征收过度沉重的税赋。
在希腊,早于秦始皇一个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列举了“保持专制政治的古代法规”, [232] 这些法规就好像是对法家和秦始皇政策的描述。繁重的税赋和巨大的公共工程“全部由人民承担,致使他们贫困不堪”,这就是结论。亚里士多德说,暴君也禁止教育,并且“一定禁绝自由集会或其他的讨论聚会”。与此相当一致的是,韩非子谴责学习,宣称在学习上花费时间就等于是减少了有用处的工作时间,妨碍了人民去完成使国家强大和使君主富裕的义务。“所以,在一个国家里,如果君主头脑清醒,就没有文学”。 [233]
事实证明,学者们(其中儒者占主要部分)难于认同秦始皇的极权国家。他们甚至鲁莽地批评始皇帝,这种做法被秦始皇认为是“绝对恶劣透顶”的。 [234] 学者们首要的批评据说是直指以下事实:秦始皇没有分封他的亲戚并且不遵从古道。 [235] 如果这种批评是真的,那就说明这个时代的儒生的确很浅陋无聊。即便如此,学者们还是给当政者制造了足够的麻烦,以至于有人认为有必要阻止他们蛊惑人心。李斯提出的建议得到了批准,这就是,为了防止“在人民中间”传布“怀疑和混乱”,人民手中除了医药、占卜和农业方面之外的所有书籍都要被焚毁。那些不抛弃他们的书籍的人都将被处以烙刑和派去服苦役。政府的禁令还说,从今以后,所有胆敢讨论《诗》、《书》的人,或者“以古疑今”的人,都要被处死。 [236]
很难确定到底有多少人因为禁书令而丢了性命。另外,就在颁布禁书令的第二年(西元前212年),秦始皇又下令活埋了460位“学者”,但这显然仅仅是要发泄他的怒气,因为他得到报告说,一些人在批评他。当然,有许多这种“学者”其实只是江湖术士。不过,一些真正的儒生显然也惨遭劫难。 [237]
因秦始皇的“焚书”而丧失的文献数目可能被夸大了, [238] 但是,在秦王朝的统治下,当政者对儒学的迫害很可能把儒学的影响力增强为一场运动,而不是相反。然而,法家对儒学的真正伤害并不是进行镇压,而是对它的曲解和滥用。人们已经认识到,就其性质而言,在汉代权威的儒家正统学说中,法家思想的分量并不少。其实,荀子就已经在主张政治独裁主义,赞成以惩罚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这种思想显然是倾向于法家思想的。这就说明,法家思想长期以来就不断地渗透进儒学之中了。
不过,这种思想渗透的进程并非一边倒的。在《韩非子》中,有些与法家哲学相反的章节可能是儒生加入的。 [239] 但是,法家人物也玩这种游戏,并且是颇有技巧的。尽管孔子在《韩非子》中不断受到批评,但在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中也出现了后来的法家式的孔子,而且,一位孔子弟子的讲话也很像法家人物的口吻。 [240] 尽管这些故事中至少有一个明显是虚构的, [241] 但它们却还是使许多儒生深信不疑。在一个故事里,讲述法家观点的孔子出任了卫国之相,这无疑使得儒生们对这种故事更是割舍不得了。 [242]
可是,法家的真正成功是他们思想中的渣滓进入了儒家文献的中心地带。不过,这些内容到底是法家插入的东西,还是儒生中的法家倾向的表现,人们还难以确定。例如,《尚书》中的一部分篇章是后来编辑的,并且包含了某些相当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资料。 [243] 然而,对于法家人物的这方面的言行(包括就地处死一个敌人)的唯一解释就是,他们想要彻底歪曲对方的思想。比如,他们让孔子被认为是《荀子》后几篇中的一篇的作者, [244] 这毫无疑问是一位法家人物窜改了《荀子》原书。法家的伎俩是大家所熟悉的,即孔子在此被荣冠以鲁国“司寇”的头衔。
学者们早已认识到了这种伪造,但是,某些法家式的侵入并不明显。《礼记》(我们将在后面作详细讨论)中有一篇题为“中庸”的文献。尽管有许多学者认识到此篇至少有一部分是后来集成的, [245] 但它还是享受了最大的声誉,特别是自宋代以来。因为正是在宋代,它被当成是“四书”之一,而“四书”则是近代儒家正统思想的特别圣经。《中庸》所云“夫子”指的是孔子,书中有下面一段文字:
夫子说:“如果一个无知的人喜欢运用他自己的判断,如果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人愿意自作主张,如果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要回到古人的道路上去,那么,灾难肯定会降临到这种人的头上。只有天子才有资格评判礼仪,制定标准,并创制文字。在今天的帝国里,所有的车都使用有同样间隔距离的轮子,书籍都用统一的字体书写,而行为也都遵守统一的规范。” [246]
这显然是把秦代的法家思想塞进了孔子口中,并出现在最神圣的儒家经典之中。其中最后一句的用词是用来描述秦始皇的标准化措施的,这种句子在西元前221年秦国统一中国之前几乎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247] 而孔子也从来没有做出过“只有天子才有资格评断礼仪”之类的断言的。事实上,孔子根本没有正面谈到过当时还在世的帝王。相反,孔子深知,在任何文化问题上,所有的世袭贵族都需要别人的指导,这是他们的可悲之处。只有在一个极权国家里,拥有政治权力的统治者才被认为是所有东西的裁决者。同样,对“没有社会地位而愿意自作主张”的人的谴责也是纯法家的。孔子说过,他自己年轻时是“没有社会地位的”(贱,“吾少也贱”),然而,他拒绝使他的意志或他弟子的意志屈从于任何一个君主。而那种认为孔子不赞成“回到古人道路上”的人,确切来讲正是被韩非子和李斯反复谴责的那样去做的儒生。 [248]
【按:周礼不讲书同文、车同轨吗?说话、建城都有规定的好吧?】
《孔子家语》也认为孔子讲了与《礼记》同样的话;所有方面都差不多,除了以下一句,即孔子被引述为赞扬了这样的人:“生活在今天,却把他们的心思放在古道上。” [249] 到了这个地步,问题是如此地复杂,以至于没有人能说清楚孔子在此类问题上到底说过些什么,或者没说过什么。法家的影响甚至反映在《论语》中的孔子所作的一些表述之中。
《论语·季氏十六》说:“夫子说:‘大道在帝国流行的时候,礼、乐和征伐就由天子来主持;而当帝国缺乏大道时,这些事情就由诸侯来组织。这种情况发生时,在十代之内,这样的诸侯们很少有不失去他们的国家的。如果这些事情是由诸侯的大夫组织的,在五代之内,这样的大夫很少有不失去他们的权力的。当大夫的家臣掌握了一国的权力时,他们通常在三代之内就要垮台。大道在帝国之内流行时,政府就不会掌握在大夫手中;大道在帝国之内流行时,普通人民就不会议论公共事务。’” [250]
尽管这一章所强调的封建等级制度不是法家的特性,不过,法家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在这段讲话中,再次出现了这样的极权君主,他的政治权力使他成为“礼、乐”和所有其他事物的裁决者。所有的权力和文制上的创新都以他为中心,并根据等级制度传给他的属下。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有学识的和有德行的大臣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但在这样的章节却识别不出来。在《论语》的其他地方,孔子倡导教民以大道,而在这一章,民众甚至不谈论国家事务。 [251]
这一章的语言以某种方式露出了真相,证明它无疑是后来增补进《论语》的。 [252] 然而,在当今,即使是一些具有鉴赏力的学者也认为,这一章在确定孔子思想的具体方向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章还要对以下这些思想负主要责任,这就是有些人所认为的:孔子在尽力复兴周天子的权力,他也赞赏帝国的独裁主义,他本人更是封建主义的卫士。 [253]
《论语》的另一章显然也是后加的,这就是《子路十三》讲述“正名”的那一章,在其中,孔子被认为是讲述了“正名”的学说,并着重强调了政府要使用刑罚。不用说,这一章不是法家人物所写,就是受到了法家思想的明显影响。 [254] 对于《季氏十六》“生而知之”章来说,这种论断也可能是真实的。孔子在这一章被认为是这样说的:“生来就有知识的那些人是最高层次的;通过学习而求得知识的人居其次。” [255] 这一章显然是在宣传这样一种思想:圣人们(包括孔子在内)生来就魔法般地具备了一切知识。这与孔子自己所强调的依靠经验、反思和不懈地学习而求得知识的主张是非常不同的。可是,法家人物瞧不起学习,并表示不信任这样的人,他们唯一有资格受人尊敬的就是他们的学识。韩非子写道:“一个人有没有才智,依靠的是他的本性。……智慧并不是某种靠向他人学习就可以得到的东西。” [256] 这与上述《论语》讲述“生知”的那一章极其相似,而《论语》这一章可能就是在法家的影响下写成的。不过,《论语》此章在儒学内部成功地树立了圣人生来无所不知的观念,这个观念完全摧毁了孔子自己的知识论基础。 [257]
至于法家学说以其整体的严密性渗透进儒学的日期,这是我们不可能确定的。但是,这种渗透显然一直持续到了汉代。不过,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到了法家完成了他们的破坏工作之时,孔子思想的真实性质已经是彻底地晦暗不明了。
第十四章 “凯旋”
人们通常认为,汉朝的一位皇帝(汉武帝)在西元前2世纪给了儒学以官方认可,也就是把儒学确定为官方的正统思想,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正是这种思想学说会增强他的权威。既然一些历史事件的原因是那样得纷繁复杂,其中就可能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但更为真实的是,还有一种与上述观点相反的主张,认为儒学自身把它的最终成功归因于如下事实,即儒学受到了普通大众的青睐,而正是普通大众经过了多少年的努力,才几乎是强迫他们的统治者接受了儒家学说。
难得有两种政治观点如此明显地相互对立,并且经过了如此彻底的交锋——这是在西元前3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对立的双方,一方是孔子的思想,认为政府的合理与否必须由它能够给予人民的满足(不仅仅是福利)的能力来判定,而国家则是一项协作性的艰难事业。为此,教育一定要普及开来,而政府则必须由那些选拔自全体人民中间的、被证明是最有能力和最有德行的人们来管理。另一方是与此相反的法家的学说,认为每件事情都必须由君主指定和裁决;人民不必理解什么,只需要服从;他们不应该受教育,只要被弄得惧怕法律。对于后一种观点,韩非子作了简洁的表述:“那些对政治一窍不通的人们说:‘君主必须赢得民众的善良意志。’……实际上,这就等于是服从民众的命令!但是,民众的‘智(慧)’是无用的,他们都像婴孩一样(无知)。” [258]
问题清楚地摆在这里:要想建成一个成功的政府,民众的善良意志是(或不是)必要的?秦始皇采纳了法家的极权主张,认为不是。可是,这并非意味着秦始皇就是一个彻底的法家哲学家,他是否完全理解了法家思想是很让人怀疑的。在接受和表现法家思想方面,秦始皇受到了更多的个人动机的促动。
秦嬴政(后来的秦始皇)早在13岁时,就继承了君位,而此时的秦国正在进行扩张战争。他的地位使他不可能过上从容宽松的少年生活。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的母亲据说曾是个高级妓女。无论她是否做过妓女,反正在与嬴政之父结婚之前,这个女子是与一个名叫吕不韦的男人在一起生活,而且,受人赞美的是她的美貌而不是她的德行。嬴政(无疑是在他母亲的坚持之下)大量赐封他母亲后来的情人嫪毐,并授予这个男人相当可观的权力。 [259] 在嬴政20岁时,他的身为一支部队之将帅的弟弟发动了武装叛乱,但被嬴政极其血腥地镇压了下去。次年,嫪毐也策划叛乱,并带领军队进攻嬴政在首都的卫队,可到最后同样遇到了失败。无论是对是错,嬴政认为他母亲是这次阴谋的同党。诸如此类的事情无疑会使秦始皇深信,周围的任何人都是他信不过的。这样的常人很难遇到的经历,无疑还得加上他对专制控制的生性喜爱,必然使嬴政易于接受法家的思想。因为法家宣称,君主应该怀疑每一个人,并把所有的权力紧握在自己手中。
所以,当嬴政的统治地位彻底稳固之后,秦帝国就被唯一的一个人的意愿所控制,换句话说,这个强大的帝国完全服务于秦始皇一个人的想法。如果有人胆敢与秦始皇的意见相左,或者把任何秦始皇不喜欢的事情告诉给他,这个人很可能会丢掉性命,所以,秦始皇几乎听不到不同意见和不悦之事。但这并未妨碍他做出极大的努力,目的是要依照他个人的意愿治理一个大帝国。他下令在石碑上刻下对他的颂辞,并把这些石碑树立在全国各地。在这些碑文中,秦始皇告诉我们,他如何消灭了强力和残暴(“烹灭强暴”),他的仁慈如何扩展到一切东西(“赏及牛马”) [260] ,以及他如何为帝国的利益而辛勤工作。事实上,是他自己做出所有重要的决策,而只允许他的官员们作一些小得可怜的创新。据说他坚持亲自监督政府日常工作的每个细节,以至于达到这样的程度:每天要亲自审阅重达一百磅(竹简)的政府文件,直到阅罢才去休息。秦始皇死的时候才50岁,但从表面上看,他确实是为了不懂得对他感恩戴德的人民而工作致死的。然而,所有这些努力最终都被证明是无效的。因为,个人的心智无论如何卓越,个人的工作无论如何辛劳,都不足以领导一个国家。
然而,就外在表征而言,秦始皇的政治事业显然是相当成功的。从他在西元前221年完全征服中国算起,到他西元前210年死去时为止,全天下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武装叛乱。只是在一个受宦官(赵高)控制的软弱无能的少年(秦二世)的统治下,秦帝国的分崩离析才接踵而至。不过,即使秦始皇还活着,大规模的叛乱也迟早都会爆发。这其中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首先,当和平在多少年无休止的战争之后来到时,确实是有过普天欢庆的时刻,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下,任何和平似乎都好于战争。战争结束后,始皇帝没收了天下人手中的武器,并把所有他认为有可能或者有能力造反的人迁徙到首都附近,以便于监视和约束。然而,即使是有了这些预防措施和最残暴的镇压手段,也保证不了完全的平安无事。在他极其残酷的政治压制之下,相当多的人逃到深山老林,变成了亡命之徒。 [261] 那些因为害怕杀头而蛰伏不动的人们,以及因为等待机会而保持缄默的人们,都在积蓄着他们的仇恨。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就会以儒家传说中的“真王(真命天子)”反对他们的统治者。
事实上,正因为秦始皇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家人物,他也就不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反儒者。他确实是杀戮了一些儒生,那是因为他要消灭那些有批评他之嫌疑的人。但是,他在树立一块自我歌颂的石碑之前,曾就碑文的内容“与鲁地的儒家学者们进行商议” [262] 。在他的种种碑文中,他把法家和儒家的思想和语句相混杂。他使用《诗经》和《尚书》的措辞,而其中一处竟婉转地提到了《论语》。 [263] 秦始皇把所有思想派别的学者都召来为他服务。即使在儒书被禁之后,他还继续让儒家学者待在他的朝廷里,直到他生命终结之时。 [264] 秦始皇并不反对儒家的学问本身,而是不赞成民众拥有这种学识,因为这样的民众会制造出使他怒火中烧的麻烦。
不论秦始皇对儒学的真实态度如何,儒生们却对秦始皇日渐厌烦起来。至少有一些儒生批评秦始皇没有分封他的亲戚、子弟。在此问题上,孔子可能会与秦始皇站在一边。因为,如果在秦代还继续实行西周封建制,就容易导致政治混乱,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但是,这个时候的儒生却远比他们的孔夫子更保守。秦始皇可能更注意这样的事实:某些儒生具有足够的勇气批评他的整个政策,并“在普通百姓中煽动怀疑和混乱”。这导致他下令禁止普通人拥有儒家的书籍和禁绝儒生宣传儒家的学说。 [265] 另一方面,儒生的影响之所以受到各方的重视,可能是源于这样的事实:据记载,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曾经警告他的父亲说,对孔子追随者的迫害会“使帝国动荡不安”。 [266]
作为惩罚,扶苏最终被他的父亲流放到了北方。不久之后,秦始皇去世,宦官赵高就与法家人物李斯共谋,伪造了一封秦始皇的书信,迫使公子扶苏自尽了。他们接着扶植起了扶苏的软弱的兄弟做皇帝,这就是秦二世。
首先举起造反大旗的是一位农民,他的名字叫陈涉(胜)。像他之前的许多人一样,陈涉被朝廷征用去服劳役,但在路上被大雨所阻,从而耽误了时间。根据秦朝的法律,陈涉本人,以及与他一起被征用之人因此就得被处死。陈涉说服了他的同伴,既然他们无论如何只能一死,就要尽量以昂贵的价格付出他们的生命。在这个时候,整个中国只需要一个火星就能燃烧起造反的熊熊大火。陈涉他们揭竿而起,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东部地区。人们踊跃加入陈涉的队伍,而陈涉马上就得到了“楚王”的称号。
尽管陈涉只是个农民,但他却是野心勃勃和聪明能干的。他深知,以他的出身,要想赢得领袖的地位是不容易的,所以,他甚至想方设法地利用迷信手段争取他的追随者的思想共鸣。一方面,陈涉竭力让他的追随者们相信他受到了神灵的保佑;另一方面,他又宣称他拥护的是被谋杀的公子扶苏的事业。 [267] 秦始皇的这个儿子之所以被人喜欢,是因为他批评了他的父亲,这也使人想起,他曾被认为替儒生作过辩护。可能是因为儒生很得人望,所以,陈涉就命令孔子的第八世孙做了他的一名顾问。 [268] 据说,在陈涉的义旗刚一举起时,东北地区的儒生和墨者就汇聚而来。 [269]
客观地说,关于儒学早期历史的资料是相当缺乏的,而如果考虑到这些资料在后来的重要性,这种缺乏就更令人惊讶了。《史记》上说,从孔子时代到秦朝,除东北地区的齐鲁之地以外,儒学在其他地方并未受到尊崇。 [270] 不过,儒家思想也在逐渐地传播,它的影响已经不限于富有阶层和有权者中间了。比如,在现在江苏省北部,有一个非常卑贱的人(可能是个农夫)的儿子,在秦代就曾跟随荀子的一位弟子学习《诗》。 [271] 儒书被禁和儒家学者被秦始皇所镇压,可能极大地增加了儒者的知名度。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谁,只要是秦始皇的敌人,就是人民的朋友。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于加入他的造反队伍的许多儒家学者,陈涉都非常欢迎,并把孔子的一位后人当作“有广博学识的学者(博士)”官员安排在他的行政机构中。不久以后,当事实证明秦国的军队要比农民之王的力量更强大,而且陈涉也兵败被杀之时,孔子的这位后人就随他死去了。 [272]
可是,这场革命还在继续。就在秦王朝极权政府陷于一片混乱之际,尽管相对来讲的可谓民主统治的首创者已经死去,然而,两种原则之间的斗争并未停止。拥护它们的两个新的卫士出现了。这一次,他们每个人都身处革命者的行列之中。
陈涉死后,革命的领导权实际上应该自然地归于项羽,可是,他并没有去承继这种有名无实的统治。项羽的祖先世代是楚国的将军,并在楚国享有封地。项羽本人是一位出色的将帅,据说由他亲自指挥的战斗从来没有失败过。项羽极其气势逼人,“当他进入军营时,没有人不用膝盖前行,也没有人敢抬头看他”。 [273] 我们被告知,在战斗中,他只要一眼扫过去,就足以吓倒最强大的敌军,并使马匹因恐惧而飞奔。他很喜欢屠杀,事实上,他是历史上的大屠杀者之一。有时他公开杀人,有时是暗杀,有时他成批屠杀投降了的士兵(据说有一次是20万人),而有时还会不问青红皂白地残杀占领区的全部人口。特别是那些没有对项羽表现出勇敢和忠诚的人,就会被项羽烹死或烧死。有一次,一个13岁的孩子劝止了他对一个被围城邑的人民的屠杀,这个孩子指出,这种屠杀只能加强另一个城邑的抵抗。实际上,他自己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史书的记载中,项羽似乎没有什么高尚的或无私的举动。
在临死之时,项羽宣称:“是上天毁灭了我,我没有犯过军事上的错误!”令他一直都不能理解的是:尽管他战无不胜,为什么那些支持过他的人都逐渐离他而去?但其他人却是能够理解的。在下一个世纪,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他借口说自己的行为是至高无上的君主的做法,其实是要用残暴的力量征服和治理天下。” [274]
要做一个相对的民主统治的斗士,这是一个很少有人能够担当得起的角色。在那个时代,这一角色的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历史上众所周知的汉高祖。汉高祖本是个农家子弟,既懒惰又傲慢,是那种“不是被推上绞架就是要登上王座”的少年。因为具有领导才能,他担任了管理几个村庄的小官。不幸的是,他还是一不小心犯了“罪”,根据秦律,他可能会被处以死刑,于是,他就逃到荒山野岭,成为头领。反秦革命爆发时,他加入其中,并被推举为将领。秦朝灭亡后,汉高祖和项羽打了4年多的仗,以决定谁来做皇帝。
【按:不能称汉太祖是匪首,匪首是专用称呼!】
最初,项羽占有优势,他拥有较大的权威,控制着更多的军队,也比汉高祖更有军事谋略。但是,汉高祖更为明智,这使他情愿并且急于得到别人的良好劝告,同时,他也知道如何在他的部下和普通百姓中取好。汉高祖通过多种方式使人民感觉到他是他们的朋友。项羽一直在劫掠和屠杀人民,而汉高祖则尽力约束他的士兵,要求他们善待人民。汉高祖每到一个城邑,就召集当地的老者座谈,向他们解释他的目的,以便建立起广泛的支持基础。他给他的士兵提供棺木,把他们的尸体送回家乡。他做了皇帝之后,就解放了“那些由于饥饿而卖身为奴的人”, [275] 并一再宣布种种大赦和免除赋税。他允许人民使用那些秦统治者对他们关闭的猎场和鱼塘。所有这些都与秦朝皇帝和项羽的做法形成最尖锐的对比。
汉高祖能够较为令人相信地做一个“普通人的朋友”,因为他本来就是个普通人,并且自己也从未忘掉这一点。他的源于普通之人的粗鲁作风明显伤害过有教养的人,但他无疑也使他的大多数臣民很快活。一位官员为他建造了一座巨大而奢华的宫殿,他反对道:“许多年来,天下充满了受苦受难者的呼号。……为什么你要建造这些超出标准的宫殿呢?” [276] 这些话语中透露出了真诚的声音。
汉高祖并非因此就完全成为一个可钦可佩和仁慈宽厚的人。他是个机敏的政治家,能够无情地消灭那些他认为威胁到他的权力的人。但他也有足够的精明,懂得如果他想保住自己的权威,就不要让人觉得他是专横的和暴虐的。在以前的统治者们激发恐惧的地方,他尽力制造友情;在他们惩罚不忠者的地方,他经常尽力以宽厚去化解或缓解之。 [277]
当汉高祖第一次占领包括秦朝都城咸阳在内的关中地区时,这个基调就已定下。他可能想过用利剑对待当地的居民(后来项羽就这样做了),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并宣布他要废除秦朝的法律。他说:“父老乡亲们,你们在秦律下遭受苦难的日子已经够久的了。……我就将与你们约定一个新的法律规章,它有三项条款。” [278] 在此,重要的词语是“约定”。因为是对秦朝人的重新征服,汉高祖完全可以如人们预料之中的那样制定法律,但他取而代之的是与他们的“约定”。在此问题上,当时的民众根本没有真实发言权这一事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汉高祖对民众的这种态度是没有先例的。在随后的日子里,汉高祖又让他的官员在每个地区挑选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让他们代表当地民众说话,并辅助行政官员的工作,这无疑是一种推动与项羽进行斗争的宣传。然而,不管怎么说,民众在政府中还是有了一定的发言机会。 [279]
在得到江山之后,汉高祖曾当众把他的成就归功于他的谋士、大臣和将军们,并声称他自己只有判断形势的能力以及用人的才能。 [280] 甚至在他作为皇帝的权力已经稳固之后,他还坚持这个托辞。这种说法至少是说他奉行的不是他自己的冲动而是别人的建议。当然,处在像汉高祖那样的地位,如果他要得到他想要的建议可能并不困难,但是,这种做法对政治理论的影响才是带有根本性的。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政治原理(从此以后就成为中国政治的基础)就是,“皇帝自己不管理日常工作,但他挑选和监督他的大臣,让他们去做……” [281] 在紧接着汉高祖的几个汉朝君主的统治下,这项原理从理论上限制了皇帝在实际政治中的绝对权力。当然,这种原理是相当儒家式的。
德效骞指出:“汉高祖的登基标志着儒家思想的胜利,这种思想是说,帝国的权威是有限的,它应该为人民的利益而行使其权力,并且应该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之上,这就超越了法家的专横和绝对君权的观念。” [282] 他指出,汉高祖开始时是一个轻视儒生的粗鄙的农民,但是,他最终却身处儒家影响的漫长历程之中,而儒生们也逐渐感觉到了这一点。 [283] 汉高祖可能从未克服掉某些未受过教育的人对书呆子的猜疑。 [284] 然而,他的一个弟弟——一位随荀子弟子学习过的儒生(刘交),却是他最亲近的谋士之一,而他的一些最好的谋士也是程度不同的儒家人物。他们一直以非凡的努力使他们的君主儒家化,有一位(陆贾)甚至为此目的而写了一本书(《新语》),并深得汉高祖的欣赏。 [285] 既然汉高祖认为纯粹的学究没有什么用,他也就不会与这样的学究相处。但是,大部分能使汉高祖接受其劝告的儒士都谙熟社会常识及其作用,能够为汉高祖出谋划策。毫无疑问,正是后一种事实才吸引了汉高祖。
在与项羽的长期斗争期间,有人劝告汉高祖(其用语使人骤然想起《论语》和《孟子》的语言),要宣称进行一场反对他的对手的圣战。汉高祖马上依计而行,发布了一个公告,断定项羽是“无道”的。用这种方法,汉高祖能够为他的事业招集无数的归附者。以汉高祖的名义发布的另外一些公告也具有明显的儒家倾向。另外,这种儒家倾向还真实地表现在他的属下请求他做皇帝的话语中。对于这个请求,高祖在以贴切的自贬语言作了一番推辞之后,还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接受了下来。 [286]
汉高祖之所以如此让步于儒学,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将是深得人心的,因而也是政治上的明智之举。当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出现麻烦的时候,高祖确实认识到,儒学的这一特点已经变得特别清楚了。事情的起因是,高祖显然逐渐不喜欢他的妻子吕氏了(她后来表现为一个极端残忍和疯狂复仇的人)。而且,他也担心他的儿子太软弱(后来证明确实如此)。他想改变君位继承人,但却受到了大臣们大规模的劝阻。这种劝阻的出现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某些没有被高祖本人吸引过来的儒生(“商山四皓”)现在成了太子的支持者。德效骞说:“因此,高祖最终屈服于儒学的影响力了。” [287]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派别的哲学家都被弃置不顾了。道家思想尽管到此时更缺乏哲学味道而成了种种粗陋迷信的混合体(即“黄老之学”),但在当时的社会和思想领域中仍然是重要的思想潮流,甚至在前汉时代的某些时期,这种思想还在宫廷中占据了优势。各种各样的宗教和哲学都被朝廷所容纳。法家思想虽然从未形成一个受到广泛拥护的“学派”,但却依旧是政府的许多实际政策的思想基础。苛繁的秦律在大部分地区仍然有效,尽管高祖也曾发布命令废除这些法律。例如,禁止拥有书籍的法律,直到他死后才被取消。
实际上,政府必不可免地仍旧实施着法家的治国之道,因为儒者没有治理一个大的中央帝国的经验和方法。官吏的使用和具体的管理措施不得不沿用秦朝的惯例和制度,结果是,政府官员的许多工作作风依然是秦法家的。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被清楚地划归为儒生或法家人物。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儒家哲学早已开始承受其对手的巨大影响了。
不过,儒学思想的影响力在稳步增加,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是,儒生是宫廷礼仪的保存者,为此,即使是粗野的农民汉高祖,最终都认识到必须得召见他们,以利用他们独一无二的长处。更重要的是,儒生几乎是古代文献和文化的唯一的看护人,所以,他们通常会是年轻皇帝(太子)的私人导师,这就保证了他们的影响力易于代代增长。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主张建立相对温和的甚至是相对民主的政府,反对暴虐的和专制的统治。尽管普通百姓并不知道像《论语》和《韩非子》这样的书,但他们对于温和之政与暴虐之政之间、对于轻徭薄赋与实质上的剥夺其生计之间的不同,却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就有许多儒家学者告诉他们说,在上述的不同之中,前者是古代圣人和孔子的方法,后者则是法家和秦朝的做法。另外,许多儒生出身贫贱, [288] 这使得他们的言语能够被人民所接受。
在汉高祖之妻吕后(雉)的家族企图继承王位时,汉王室建立起来的民心所向的重要性集中体现了出来。汉高祖死后,吕后逐渐巩固了她的家族在朝廷之中的权力,并最终利用欺骗性的手段,让吕氏家族中的一个人(据说仅仅是个婴儿)做了皇帝。可是,大臣们并不认可吕氏的这个举动。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如下问题:帝国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呢,还是只有得到了大臣们的同意,这种权威才能贯彻执行?当吕后在西元前180年死去时,她的家族与汉室之间立刻爆发了冲突。此时此刻,一支部队中普通士兵的忠诚成了问题的关键。士兵们被要求在吕氏和刘氏两个家族之间做出选择,结果是他们宣布忠于刘氏的汉室。 [289] 接下来,大臣们就全部消灭了叛乱的吕氏家族,并邀请汉高祖还在世的年纪最大的儿子(代王刘恒)来首都继承皇位。这位皇子害怕这是个阴谋,但他的一位官员告诉他不必害怕,因为有以下理由:“汉朝兴起之时,去掉了秦朝的苛刻而令人烦恼的东西,减少了一些法律和条令,并表现出了他的德行和仁慈。所有的人都很满意,并且任何力量都难于动摇他们的忠顺。”这位官员提请皇子注意这样的事实:普通士兵都宣布忠于汉室。他又劝说道:“即使大臣们想改变(汉室),普通百姓也不会答应让他们役使。……您的贤明、您的圣德、您的仁厚和您的孝顺(所有这些都是儒家的美德)是哪里都知道的。因此,大臣们是根据普天下人的愿望而自愿欢迎您并要您继位的。”这位皇子终于继承了大位,成为汉文帝。 [290]
在所有的中国皇帝中,汉文帝很可能与孔子最为投缘。这并不是说汉文帝是个教条式的儒士。汉文帝不是这样的儒士(孔子也不是这样的的儒士),但是,他的治国精神却真的是孔子式的。 [291] 德效骞认为:“汉文帝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儒家学说,认为统治者就应该为他的臣民谋福利,并把儒家学说付诸实施。他减少税赋,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他节约个人开支,避免任何形式的好大喜功。……他请求人民对他的施政提出批评(他的这种请求是真诚的),他还寻求有才能的平民帮助政府机构工作。他……对饥荒和经济萧条极其忧虑,甚至取消了耕种田地的土地税,而他的继任者则在不久之后又恢复了以前的做法。” [292] 汉文帝制定了由政府开支赈济饥荒的具体措施,并为上了年纪的人提供养老金。他为了这些目的而使用的方法部分仿效了《孟子》推荐的做法,他的一些诏书也引用了这本书,尽管没有直接点出书名。 [293] 他颁布了一个解放政府奴隶的诏书。 [294] 他取消了对批评政府和皇帝的人施以处罚的法律,认为这样的法律使得君主不可能“听到对他的过错的议论”。他废除了毁伤肢体的刑罚,并大力整顿司法秩序,使死刑在当时变得很少见了。他严肃认真地考虑过把王位传给他能找到的最有才干的人,而不是他的儿子。根据他颁布的遗诏,他的葬礼要精简到绝对的最低限度。他不希望因为他的丧葬搅扰人民,并认为他的死应该使人感到喜悦而不是忧伤,这是因为他做到了不犯严重错误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295]
这样的一个皇帝似乎是好得有些不太真实了,但是,有充足的证据说明,这样的场面是真实可信的。汉文帝在位期间,人民的生活无疑比过去(或不久的将来)更能过得下去了。整个国家繁荣昌盛,人口稠密。然而,如果说文帝是讲究道德的,那么,他也具有儒学的不足。尽管孔子不是绥靖主义者,但他还是更信仰道德的主动力量,而不是被迫做出的保证,而在儒生们那里,这种信仰变得很高大。汉文帝止住了国家在社会安定和经济活动两方面的衰退,而西北的匈奴则利用这种内强外弱的形势,日甚一日地展开了深入内地的武装袭击。
汉文帝是很迷信的,但这还不足以使他与他那个时代的大半儒生相区分。在他的朝廷里,既有儒家学者,也有其他哲学派别的学者,而且他还任命了一位法家人物做太子的私人导师。 [296] 但这位继承人(汉景帝)在位时的表现并不特别引人注目,只有以下事实除外:在他的法家导师的鼓动下,随着帝国政府实力的大增,曾以某种改头换面的形式存在于汉代的封建主义几乎被扫除干净,再也不是国家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了。可是,下一位皇帝,他在位初期却是处在强大的儒家势力的影响之下的,这位皇帝就是声名赫赫的汉武帝。
汉武帝是所有中国皇帝中最重要的几位之一。他在位期间对儒学的历史具有突出的重要性。他使儒学得到了国家的认可,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这一举动堪与康斯坦丁大帝(Constantine)对基督教的信仰相提并论。汉武帝 [297] 受过很好的文学训练,他的诏书具有明显的儒家偏向。这些诏书一再讲到他对普通大众的关切,强调了礼、乐和学习的重要性,还引用了《易经》和《论语》。 [298] 在他的文化政策激励下,人们重新发现了许多古代文献,特别是儒家经典。
在他继位的头一年,汉武帝批准了一个值得纪念的提议:在一批被推荐做官(“举贤良”)的学者中,去掉了那些研究法家学说的人。他为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中的每一部经典都设立了“博士(博学的学者)”的官职,并为每一位博士提供了教授50名学生的生活费用,而这些学者则是朝廷中的官方学术代表。这项政策为帝国大学(太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随着时代的推移,政府中的大半低级官员都要从太学那里选拔,这个事实确保了政府能够日渐被儒学所渗透。汉武帝在位时,还利用不断考试的方法选拔有学识的人员进入政府,他还给孔子的两位后人封了官。他任命的政府宰相以前是猪倌,而现在却以其对《春秋》的精深研究而获此殊荣。所以,毫不奇怪的是,许多学者都把汉武帝的在位时期确定为儒学的凯旋时代。
然而,与秦朝以来的政府相比,汉武帝的统治也是更为集权、残暴和专制的政权之一。汉武帝反对以前的宽松统治,因为他认为,在较为宽松的政策之下,帝王不得不严重地屈服于大臣的劝谏。所以,汉武帝就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把政府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既然在这种倾向明确出现的同时,儒学也逐渐得到了官方的支持,那么,就无疑会有大量的学者(包括某些最具批评精神的学者)自然而然地认为(并且是一直这么认为),那种认为皇帝应该进行专制统治的理论是儒学的学说。其实,在汉武帝朝廷中,有一位并非儒生的高级官员就声称,在儒者看来,“君主定调,大臣奏乐;君主前行,大臣随后” [299] 。
从汉武帝时代以来,许多儒者确实是持有这种观点的。较早的儒学,甚至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也被曲解为抱有这种态度。因此,既然汉武帝的统治对于人们如何解释和理解儒学甚至是孔子本人的思想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就必然要求我们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审视在这个时代实际发生的事情。
汉武帝15岁时登基。那时,他的主要大臣都是儒生。正是在这些儒生的影响下,汉武帝去掉了被荐做官的那些法家和别的学派的学者。这些儒生大臣还把一位受人尊敬的儒者(申公)请到朝廷,而武帝则向他请教如何治国。但这位老学者有些奇怪,他曾被一个皇亲严厉惩罚过(可能是宫刑)。他简短地回答说,搞政治是行动的问题而不是多说话的问题,而这位少年人君此刻正热衷于文学研究。汉武帝虽然被这种回答给触怒了,但还是很客气地招待了这位年迈的客人。 [300] 不久之后,儒家集团就被皇太后剥夺了权力,而这位皇太后是道家的信徒。尽管在不久之后,特别是这位皇太后死后,儒生们又回到了朝廷的高层职位中,但汉武帝对儒学的热情却变冷了。
汉武帝对于儒学之态度的变化是有几个基本原因的。除了与宫廷政治中的争权夺利不无关系以外,儒学的一贯主张也是重要原因,那就是:君主的职责就是给人民带来福利和幸福,一旦他不去这样做或不能这样做,他就不配在位。这种学说为革命者所用,并且汉王朝的缔造者也曾使用过这种思想。因为同样的原因,这种学说对于当朝的皇帝肯定也是一种威胁,特别是如果他想要进行专制统治的话。在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的朝廷中,一位道家人物主张:古代圣王们(他们是受到儒生赞扬的历朝历代的缔造者)事实上只是弑君篡位者。一位儒生就此问道:这样一来,汉代缔造者的地位会是什么样的呢?汉景帝马上制止了这场辩论,这就强烈地暗示着,那些避开这个主题的学者会寿命长一些。一位当时的史学家写道,“从此以后,没有学者胆敢”讨论这个问题了。尽管那位同样率直的儒者被推荐给了汉武帝,但他在汉武帝的朝廷上却并未得宠。这一事实是意味深长的。 [301]
所有伟大的儒家大师——孔子、孟子和荀子——都明确主张,君主应该把政府行政管理托付给有德行和有才能的大臣,而这些大臣则必须首先忠诚于原则,忠诚于大道,而不是忠实于君主个人。他们也都认为,如果君主行为不当,称职的大臣就应该站出来反对。 [302] 对于一个像汉武帝那样日渐表现出专横和暴虐倾向的人来讲,这种主张自然是令人厌恶的。
不过,假如儒生们真的具有实际管理政府的能力,他们也会得到某种程度的谅解,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具有这种能力。他们早已逐渐专注于纯粹的书本研究了,这与孔子的明确警告是背道而驰的。 [303] 这样的儒生还深深地沾染上了道家形而上学的习气,以至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把管理政府的技能看成是一个巨大的魔法体系。儒家的敌人,有时甚至是儒家的朋友,都把这样的儒生看作是思想狭隘的学究,认为他们要么是没有经历过政治实践的训练,要么是对于管理伟大帝国所必需的政治事务缺乏理解。 [304] 儒生们也轻视了王国周遭蛮族大兵压境的真正危险,还把汉武帝雄心勃勃的军事策略谴责为使国家不必要地陷入穷困的纯粹的帝国主义。他们坚持认为,如果皇帝一门心思地增进他的德行,并支持和偏爱像他们这样的儒生,蛮族之人就会甘愿俯首称臣。 [305]
对汉武帝来讲,儒生们确实是让人头疼的,这种感觉与当年的秦始皇一样。但是,汉武帝很熟悉秦始皇这位专制前辈的经验,那就是,只要儒生参与了对他的王朝的破坏活动,他就镇压和处死他们。但是,与秦始皇相比,汉武帝的整体策略显然是更为巧妙和有效的。
汉武帝的这些策略明显地表现在了他对待儒家学者董仲舒的态度和做法上。董仲舒是研究《春秋》的知名学者。在上一代皇帝的统治下,汉朝廷发展出一套制度,就是让各级地方政府把学者们从全国各地推荐到朝廷做官(举贤良文学之士),有时还要对他们进行考试,合格者才加以任用。汉武帝继位初年,董仲舒是几百位被推荐给朝廷并由皇帝亲自对他们进行考试的学者之一。这场考试和董仲舒的答卷被保存至今。
在这场考试中,汉武帝开头就说,他最勤奋地专注于思考关于良好政府的问题,但当他考究以往的历史进程时却发现了一个令他吃惊的难题,这个难题是:是否可以说认真仔细地“效法上古之制是无益的”。他希望聚集而来的学者们就他提出的这个问题进行评议,而不要有任何隐匿。 [306]
董仲舒在他的答卷中告诉皇帝说,他根据《春秋》的例证发现了治国的方法。他解释说,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唯一必须要做的是观察自然现象,并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寻求与自然现象的警示保持一致。如果政治无道,上天就用降下比如洪涝、饥荒或冰雹之类的自然灾害来警告君主。他坚持认为,《春秋》这部书就包含了关于政治哲学的深奥学说。他引述该书的话说:“在春天,第一个月(正月,‘春王正月’)是由皇家历法规定的。” [307] 依靠一个双关词语——“正”,董氏解释了这类字的深刻含义。 [308]
董仲舒也激烈批评了政府管理,认为汉代保持了秦朝法家的做法。“现在的做法是,废除那些运用先王之德教的官员,把对人民的治理完全交给了那些使用刑法的人的手中——这就不是完全依靠刑罚治国了吗?孔子说:‘不首先教育人们就把他们处死,这是残酷虐待的行为。’” [309] 尽管董氏接着就用对皇帝之德的称赞弱化了这种批评,但他还是主张,如果没有合适的教化,其他的政治作为都是无济于事的。他提出应该为此目的而建立一个国立大学(太学),并要求政府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汉武帝并不十分满意这样的回答,所以,他要求把这场考试继续进行下去,并写下了一个具体的批评意见。他说,受到学者赞誉的先王们事实上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治国方法。这些治国之道,有的是积极进取的,有的是宽松无为的;有的时候使用严刑峻法,而在另外的时代,监狱却是空空荡荡的。汉武帝说,他对此大惑不解。他说,学者的论文并没有给予他多少帮助。他们学识渊博,但他们的建议“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是难于付诸实施的”。他要求他们再来一次。 [310]
对此,董仲舒还是以同样的指导思想进行了策对。他认为,圣王之间的不同只是表面上的。他再次主张,为了造福于人民,应该设立太学,以便支持学者的研究和教学。他也提出,应该建立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以便任用良好的官员。皇帝对此回答还是不满意,他说,学者博学于古,但问题是,“你们为什么对当今的事务却那么糊涂呢?” [311] 他再次要求他们做出回答。董仲舒重申了他的主张:过去与当今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他也再度抨击了政府的一些措施,谴责了暴虐的执法。董氏认为,皇帝宠信的官员靠着从事只能由政府掌握的垄断贸易而发了大财,但人民却饱受折磨。最后,他请求禁止除了儒家学说之外的其他所有学说。 [312]
要是换了秦始皇,会因为这种批评而活埋了董仲舒。但汉武帝并不想让这样一位杰出的儒生成为殉道者。汉武帝有更好的办法,他给了董仲舒一个高的官职。但是,我们一定得问一问,这是个什么官职?
汉武帝有一位兄长,他的封国在东南地区。这位兄长是个武夫,一个喜欢招揽刺客的狂妄自大的寻衅滋事者。要是让他待在皇帝身边,肯定会招惹出种种麻烦。汉武帝派董仲舒去做这位兄长的丞相,也许认为把这位喜欢布道的学究派到他的傲慢的兄长那里肯定是个极有趣的玩笑。另外,既然这个封国之王经常杀掉那些惹他不悦的大臣,汉武帝很可能也希望,这样一来,他就再也不必见到董仲舒了。如果武帝真是这样想的,那他就错了,因为董氏最终驯服了这头“狮子”,并在他的职位上大获成功。后来,由于董仲舒的一个政治对手的怂恿,汉武帝又把董仲舒派到了另一个封国,而这个封王是汉武帝的一个更为残暴的兄长。这一次,董仲舒不久之后用辞职救了自己的性命,理由是“因为健康的原因”。此后,董氏以一位退休学者的身份赋闲在家。武帝倒是不断派使者来向他请教对国事的意见。可是,这位皇帝是否会按照董氏的意见行事却是令人怀疑的。 [313]
汉武帝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免受董仲舒的执着抗争的严重打扰,同时,武帝不仅避免了使董氏成为烈士,而且还享有这位著名学者的保护人的美誉。事实上,这位皇帝还曾宽宏大度地“救了他的命”,那是因为董氏写了一部“愚”书而被判死刑,而武帝则赦免了他。 [314]
汉武帝主持的另一次考试策问也被保存下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喜欢的那种儒生。这次是对公孙弘的策问。此人年轻时是个监狱看守,但却因为某次失误而丢掉了这个职位,并且不得不去养猪。他40岁时开始研究《春秋》,60多岁时因被举荐而得到了官职。他因为轻率地不迎合汉武帝的看法而被免职,但随后又一次受到举荐,并在西元前130年得到了策对的机会。
在这次策对中,汉武帝虽然使用了儒家的语言,但却是明确地为学者们表达非儒家的观点开了一个头。他问道,为什么在古代圣人的治下还有灾害?而儒家的仁、义、礼、智等德行又如何才能付诸实施呢? [315]
公孙弘以正统儒家的方式开始了他的策对,强调的是诚信的重要性。然后他列举了“政治的八项原则”,不过,他的这些原则中的后两项——罚和赏——明显是法家的主张。由此开始,他的文章读起来像是一篇法家的文章。他也叙述了仁、义、礼、智等儒家四德,但其用词更像是法家的而不是儒家的。他使用的多数专用术语直接出自《韩非子》。他认为,为了治理好国家,国君必须立法,并使用“术”(法家词语)。君主必须“垄断控制生死的手柄”(《韩非子》第48篇中一节的意释),并严格保持君主个人对政府的控制。 [316]
评定策对之名次的官员无疑很反感公孙弘的这篇隐藏着法家真义的文章,就把它列在了一百多篇对策文章的最后。这个排序发生在把这些文章送交汉武帝审阅之前。可是,汉武帝却很欣赏公孙弘的文章,并在审阅后把它的排名挪至首位。 [317] 这一做法并不令人惊讶。到那时,汉武帝实际上是越来越厉害地使用着法家之术。早在他考查董仲舒之时,汉武帝就显示出了对于《韩非子》的相当了解。 [318] 几年之后,在一份诏书中,汉武帝引用了法家人物李斯的奏议和《韩非子》, [319] 但却并没有明确提及每次引用的来源。因为在当时,承认自己是法家并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策略,而汉武帝在这一点上是很机敏的。但他在私下里却无疑越来越倾向于这个方向。如果他不想暴露自己的意图,他就不过是遵从了《韩非子》的告诫:“君主一定不要流露出他的思想。……听到了却没听到,知道了却不知道。” [320]
汉武帝之所以喜欢公孙弘这位前任狱吏,是因为公孙弘事实上在很多地方表现出了法家的作为, [321] 但他的真正被看重,是因为他名义上还是儒生。身在汉武帝朝廷做官的史学家司马迁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他说,令汉武帝极其满意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公孙弘“能用儒家的学说装饰政府管理中的法制和官吏作风”。 [322] 埃森·盖尔(Esson M. Gale)在写到前汉皇帝特别是汉武帝时指出,尽管“在实际的治国之道上,他们恢复了秦朝法家政治家的令人沮丧的政策”,但为了取得声望,“他们用了一些与‘儒学’相一致的东西来装点门面” [323] 。
对于这样的虚饰门面而言,像公孙弘这样的纯粹徒有其名的儒生是完美的材料。在某些时候,作为对汉武帝剧烈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反对,公孙弘立场坚定并在某一场合得到了汉武帝的让步。 [324] 可是,在大多数情形下,当双方看法不一致时,汉武帝则完全不理会公孙弘的意见。公孙弘小心翼翼地很少表现出这种不一致,并且从未与皇帝有过公开的争执——这确实与孔子的告诫背道而驰。在《论语·宪问十四》中,孔子说:“勿欺也,而犯之。”
司马迁可能认识公孙弘,他称公孙弘“是个多疑之人,外表上宽宏大度,内心里却诡计多端”。他假装与那些对他有意见的人很友好,但到最后总是要施以报复。 [325] 像董仲舒这样的耿直儒者,则称公孙弘为阿谀奉承者。据记载,某位学者就是因为对公孙弘的逢迎拍马发出了公开指责而获得了极大的名望。可是,公孙弘的行为极端小心,人们根本挑不出他的毛病。他的孝行已经无以复加,他的生活也极其俭朴,还因为用自己大部分的薪俸帮助别的学者和朋友而得到了人们的赞誉。 [326]
皇帝很快便提拔了公孙弘。在几年之内,他就位居众官之首,做了丞相,还被封了侯(平津侯)。这种没有先例的提升给所有儒家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公孙弘又成功地(而董仲舒则失败于)让皇帝建立了一所太学,这就意味着50多位儒生获得了生活保障。 [327] 这显然有利于“精明的”儒生与帝国政府进行合作。
尽管公孙弘平步青云(他周围却有许多人身首两分),并且一直担任丞相到他自然死亡,但却没有证据表明他在政府中发挥过任何有效的作用。相反,他显然是汉武帝个人专制统治的合宜的“儒家”装饰。 [328] 在汉武帝的手下,另有一些人帮助其建立和贯彻他的实际的治国计划,但是,这些人并不一定占据着政府的高位。汉武帝真正能听得进去的谋士是那些精通财政、刑法和军事的人,亦即熟知皇帝的政治利益领域的人。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位是桑弘羊。桑弘羊是个公认的法家人物,他称赞秦始皇,瞧不起儒生,甚至轻视孔子本人。 [329]
在像桑弘羊这样的官员们的辅佐下,汉武帝推行了以下的治国之道:帝国主义式的征服,极权主义的经济体制,以及对人民的法家式的压制。汉武帝的军事措施起初以蛮族的威胁作辩解,后来则扩张为好大喜功的开拓疆土。这样的南征北战耗尽了国库。为了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建立了对生活必需品(如盐和铁)的经营垄断权,货币也被贬值。为维持“纪律”,法令和惩罚成倍地增加;为充实国库,就提高地租并增加新的政府奴隶。官员们因得不到薪俸而无法生活,这种状况逐渐习以为常,以至于没有什么人再想做官了。汉武帝后来又建立了一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一个已经被任命做官的人,为避免其清白受到怀疑,就得付钱给政府。 [330] 这些给国家带来了权力和光荣的措施,意味着人民的受苦受难,但是,对政府政策的任何批评或“妨碍”,都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331] 到了汉武帝长期统治的末期,对政府的不满引发了暴乱。有趣的是,这种暴乱在孔子家乡一带很盛行,而事实上这是当时的中国最儒家化的地区。当政府对这种暴乱予以镇压时,通常都会处死上千人。 [332]
不过,如果汉武帝像秦始皇那样仅仅依靠武力并且不在乎公众意见的话,很怀疑他还能维持他的权力。不,他不是的。汉武帝制造了极大的仁慈的借口,把他的意在巩固自己之权力的种种行为说成是有着最大的利他主义动机。他的最精明的消除公众怨恨的做法就是对大批儒生的支持和资助,这些儒生中既有政府官员,又有享受国家津贴的学者。秦始皇活埋儒生,汉武帝则尽力用糖浆糊住儒生的嘴巴。
儒学的影响是相当可观的。从此时起,研究儒家经典的人数骤增。一位汉代史学家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因为现在这无疑是升官发财之道。” [333] 然而,在这种动机下,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来的新加入者,都很少是令人满意的。对当局的顺从使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渐转向了“安全”的研究和主张,远离对于社会和政治现状的“危险”的批评,这种表现成了那个时代的儒学的特征。汉武帝把公孙弘的对策文章擢至第一名的行动是一个生动的例子,通过这样的例子,政府显示出了它是如何看重正确观点的。所以,儒学内部早就在很好地进行着的专注于古书的研究是个相对无害的追求,政府则利用在策对中强调文献之重要性而对这种研究加以鼓励。沙畹写道,正是从汉武帝时代起,“中国思想界开始表现出一种倾向,即在古典文献中寻求所有的智慧原则” [334] 。
那些研究非儒家经典的学者倒是没有得到官方的任用和提拔,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起到维持儒学纯洁性的作用,而实际情况刚好相反。有大批的学者,虽然他们的真正兴趣在别处,却想方设法变成了专业儒生,接着就用他们原初的道家、法家或其他哲学的立场来解释儒学。还不仅仅是这些。正如胡适所指出的,汉武帝统治下所产生的这种儒学事实上是“一种合成的宗教,其中混杂了无数的民间迷信和礼仪崇拜的因素……上面薄薄地覆盖着儒家和早期儒家经典的伪装,以便使它们看上去显得受人尊敬并具有权威性”。但是,“这种儒学根本不是孔子所教导的或被孟子哲学化了的学说……” [335]
这个论断无疑是真实可信的。可是,同样真实的是,流行在汉代的孔子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此后千百年间人们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甚至在当今时代,人们仍然摆脱不了这种影响。实际上,在汉武帝统治时期,思想界的一切事情都受到了当局的左右,包括那张隔在我们与任何对孔子的真正理解之间的不透明的幔布。我们在此不必在意那些包括超自然事物在内的传奇的丰富发展,比如那些声称孔子出生时有龙和精灵在天空盘旋的故事,这些传说本身就是不可信的。但是,出现在汉代著作中的孔子的其他故事,尽管它们事实上简直是不能相信的,却仍然为人们所接受。作为例证,我们现在只考察两部书,《史记》和《礼记》。
《礼记》是大部头的儒家经典之一,由若干篇主要是讲述礼仪之用法的文章组成。它由汉代儒生集成,其中无疑包含了一些一定程度上的较早的文献记录。某些人有意图地想把这本书中的一些文章的产生时期归之于早至接近孔子的时代,因此,《礼记》中的某些部分一般被认为是理解孔子思想的基本资料。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些材料之后就会发现,即使是书中的最好的那些部分,至少在后来也有过很多的重新编订和增补插入,这就使得它们值得大受怀疑。比如说,篇名叫作《中庸》的那篇文章包含有法家的思想,而根据另外的一些理由,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些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庸》之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后世的作品。 [336] 然而,从宋朝开始,《中庸》就成为受人尊敬的儒家“四书”之一,其他三部“书”是《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另一篇叫作《大学》的文章。不过,也没有理由认为《大学》是完成于很早时期的作品。 [337]
《礼记》的其他部分也提到了孔子,但并未给人以多少的可信度。其中的一些有关孔子的观点可能是依据了真实的传统说法,可是,它们经过了那么多人之手,使得现存的表述形式颇为令人怀疑。其余的则是相当明显的纯粹杜撰。 [338] 《礼记》的那个长篇文章《檀弓》经常被作为有关孔子的可靠资料来使用,然而,尽管其中包含了一些颇为真实的资料,但整篇文章却很难令人相信,因为其中有太多不可靠的东西。比如说,其中所描写的孔子在其最后日子里的行为是一个牢骚满腹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和讲迷信的老人的表现,这与《论语》相关篇章中所记载的身患重病时的孔子的表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339] 根据这篇文献的记载,孔子完全是按照汉代儒家君子的颇具贵族气派的准则而行事的。正如中国的批评家所指出的,这也是与《论语》中的孔子的行为相冲突的。 [340]
出现在《礼记》中的许多地方的孔子并不是生活在鲁国的普通人,确切来讲,这本书里的孔子是在几个世纪的传统说法中被精细制作而成的圣人,以及儒家轶话中的英雄和神人。这样一来,《礼记》中孔子的一举一动当然也就像因循守旧的汉代儒生那样了。孔子先前被改宗道家和法家思想,现在则被改信了汉代儒学。
在这些著作的作用下,汉朝诸如此类的关于孔子的说法被后世之人认为就是孔子当年的真实情况。而在这些汉代著作中,没有一本能比《史记·孔子世家》编撰的孔子传记更有影响力。多半的中国及西方学者都认为,这个传记尽管有某些缺陷,但还是不失为我们现在理解孔子生平的基础。 [341] 这样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史记》中的这篇传记的首要企图,并且几乎是唯一的主要着眼点,就是把孔子的生平事件缀联为编年顺序。《史记》是由司马谈和他的儿子司马迁共同完成的,他们两人都是汉武帝的廷臣,而这部书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并且正因如此,它“在中国传统教育的必修课程中占据的位置仅次于正统的儒家经典” [342] 。《史记》中的一些传记篇章无疑是文学佳品,在这些作品中,各种人物都有着明确的行为动机,人物性格被描绘得活灵活现,偶然事件被津津有味地联系在一起,男人和女人也都是有血有肉的。
然而,与《史记》中的那些上乘作品相比,孔子的传记却是粗糙而杂乱的。在这篇传记中,并没有什么人物的动机,也几乎没有首尾一致的孔子性格的发展。事实上,它包含了一系列集自儒家、道家和法家资料来源的事件。对于这些不同来源的事件,作者既没有进行认真的批判考证,也没有把它们理顺为和谐一致的发展过程,而是以所谓的编年顺序杂凑在一起的。结果是,在整篇传记描述中,孔子像木偶一样地活动。时间和时代的错误并不是例外,而几乎是通则。孔子被描绘成与死去很久(有一次是100年)的人们交谈。有两个人(被认为是他的第一批弟子)据说是受人劝导而跟随孔子学习的,然而,他们却在尚未出生时就在孔门实际求学了,这显然有悖史实。作者似乎没有能力记住故事中的孔子到底身在何处。他说孔子离开了某国,然而却继续讲述他在这个国家的行动,随后又突然讲述了孔子在另一个国家参与了某件事情,但却没有提过孔子已经到了那个国家。正如许多学者所说,在《孔子世家》中发生的事件的年代又经常不同于《史记》其他篇章的记载。 [343]
这个孔子传记也充满了荒唐之事。一位负责军事的大臣(宋国的司马)想杀死孔子,但却使用了一种新奇的方法:他砍倒了这位圣人在下面讲过学的一棵树。但是,尽管发生了这种危险事情,孔子还是悠然而去,而这个阴谋策划也就这样被挫败了。虽然这篇传记中有上述的这些不足之处,但是,如果它所描绘的是关于孔子的一幅前后一致的、可以令人相信的人物图画,并且能与像《论语》和《孟子》这样的较早作品合理地保持一致的话,这可能还是一个让人基本可以接受的传记。但它并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它所表现的孔子是一位明察秋毫的圣人,并且经常是冗长地讨论超自然的东西,这当然就与《论语》的记述发生了直接的冲突。 [344]
《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多半故事肯定是采自其他著作。作者把这些故事合在了一处,并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它是根据某种既定的手法编辑而成的。根据这种编辑手法,作者巧妙地并且几乎是难以让人觉察地有意破坏了作为一个可钦可佩的个人的孔子的品格。直截了当地说,在这个传记中,孔子被描绘成了说谎者。作者先引述孔子说的两段话,肯定了孔子对于军事活动一无所知,但在这两段之间,作者却又引述孔子弟子冉求的话说,孔子教授过冉求军事谋略。在另一个场合,孔子又被描述为公然毁掉自己刚刚许下的诺言,当子路对此感到震惊并表示反对时,孔子被认为是这样作答的:“那是在胁迫之下做出的誓言;神灵对此并不在意。” [345] 然而,一些学者的考证结果是,这个事件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346]
这部传记中的许多事情显示出了隐含的但却确实是对孔子含有敌意的看法。这一点在它转引《论语》章节的选择上是非常清楚的。这些章节的内容都是与历史事实相抵触的,比如它作为精华地引用了《乡党第十》中的一节:“如果席子不摆正,他就不坐下(席不正,不坐)。”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使孔子在2500年中受人爱戴的那些亲切、真诚和有人情味的章节。可以说,这部传记中所引《论语》的章节中几乎没有一条是这样的。 [347]
为什么这个传记的品质如此低劣呢?钱穆力图用归咎于后人对原初文本的改变和插入来解释它的不足之处。 [348] 这个传记的原文肯定被窜改过, [349] 但这并不适合于解释如下事实:它甚至没有一本良好传记的痕迹。当崔述说这个传记“十之七八是诋毁”之时, [350] 他非常突出地指出了这一事实。这本传记中的很大一部分的确是贬损了孔子的名誉。但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这是为什么呢?
《史记》的两位作者都是汉武帝的朝臣。父亲司马谈是一位道家人物,在收入《史记》的一篇论文中,他尖锐地批评了儒学。 [351] 至于他的儿子司马迁是否也是道家人物,学者们是有意见分歧的。不过,有证据表明,司马迁至少是有这方面的思想倾向的。 [352] 然而,我们无法区分这部书的哪些部分是父亲写的,哪些部分是儿子写的,这个无法逾越的困难使得批评家们各取所需地来证明各自的看法。
尽管不能确定究竟是父亲还是儿子主笔撰写的《孔子世家》 [353] ,但是,从它选取的事件和使用的语言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个传记大量吸收了道家著作并体现出了许多道家思想。它记述说,孔子找到了道家圣人老子,并受到老子的训导。这个事件并不是历史事实,它的首创者可能是道家著作《庄子》的某一篇章的作者,其目的是提高道家的声望,损害儒者的声誉。 [354]
在这部传记的背后,极有可能存在着某种道家思想的倾向。《史记》的两位著者均是汉武帝的大臣。显而易见的是,尽管他们钦佩那种坚定持守其原则的儒家学者,但他们却非常藐视那种专门向其暴虐的主子献殷勤的儒生,他们在《史记》中把这种儒生称为“从谀之儒”。 [355] 《史记》以最直率的语言谴责了公孙弘这样的升至高位的“儒家”式的走狗。它指出,自从公孙弘做了丞相,人民所受的压迫不断加剧,执法也日趋酷烈。“皇帝把那些有贤才、有德行和有学识的人士召集到朝廷,并对他们表示敬意,其中的一些人还升至公侯、大臣和高级官员。身为御史的公孙弘被皇帝推崇为官员的榜样。尽管他盖的是棉布被,每餐只吃一盘子饭,然而,”这位历史学家却讥讽道,“这种做法并没有改进道德状况,反而使民众变得更加热衷于争权谋利了。” [356]
有人主张,《史记》的写作目的主要是批评汉武帝之政。 [357] 但这是个危险的游戏,因为司马迁有过类似的教训,那就是因为他斗胆批评了汉武帝的一个决定而被处以宫刑。当像公孙弘这样的喜欢复仇的“儒生”大权在握时,不可能在一部当时的中国通史中不写孔子,但是,要是公开批评孔子,便是最不明智的举动了。所以,《史记》的作者们很可能就选择了这样的写作方法:表面上是赞誉这位圣人,而事实上却是在巧妙而有效地攻击孔子。实际上,他们把孔子描绘成一个油嘴滑舌而又狡猾伪善的“儒者”,就像挤满汉武帝朝廷的那种儒生。这父子二人机敏地预料到,这些绅士们根本不会觉察出这种巧妙的批判。
沙畹曾认为,司马迁对孔子肯定有很高的评价,因为他把孔子的传记放在了(本不属于他的)“很高的荣誉地位”,也就是放在了“世家”这一类中,而这一类本来是记载世袭君主的。 [358] 但是,沙畹又指出,《史记》是一部讽刺性的作品, [359] 它把孔子放在他本不应该待的地方,这可能具有打趣的妙处。
说《孔子世家》是一篇精心伪装的讽刺性作品的假说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这就是:沙畹很难翻译司马迁称颂孔子的那段赞语的开头的句子。在1895年出版的译文中,他把它解释为对孔子的热情的颂辞,10年之后他又把这同一句话改译为用冷淡的称赞表现了对孔子的贬责之意。 [360]
总之,这篇传记的迄今为止的本质是:2000多年来,尽管一些人对它有异议,但还是被看作是对孔子生平的确切描述。
儒学在汉武帝治下所发生的变化对于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从那时起,在时有起伏之中,当政者继续拉拢和收买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的儒学,而这种拉拢和收买常常是极其慷慨的。那些自称为儒者中的一大部分人不可避免地变得颇为积极地对当局的愿望做出回应,而儒学也时常被政府用来作为控制甚至压迫人民的工具。政府对学术的收买在许多时期会导致“思想统一”的不幸结局。
被官方完全认可和全盘接受了的孔子思想是远离实情的东西。这种转变是难于控制的。然而,每一位研究《论语》的学者,以及在每个时代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够透过繁难的注释和官方解释的幕幛,了解到这位孤独的鲁国学者力图要道出的真实思想。当满族人在17世纪征服了全国并把一个极其残暴的政权强加给这个国家时,他们也把官方的儒学继承下来,并发展为一种思想控制术。可是,这个时期的一些最有才能的学者不仅拒绝在满族人的治下从政,而且猛烈攻击近2000年间发展起来的新的儒家学说的整个精致的结构。他们谴责埋头于单纯的学习书本,坚持认为学者应该像孔子那样,一定要要求自己关切普天下的实际政治事务。这些学者怀着充沛的活力和学术才干回到了《论语》和《孟子》的基础文本上,并反对许多早期道家人物对于有关孔子的真实记载的败坏和窜改。他们认为孔子并不是教条主义者,也没有建立那种支持帝国暴政的学说,相反,孔子是一位最诚挚的、实事求是的和看重经验的真理的求索者。这些17世纪的学者们的开拓性的努力当然并非十全十美,但他们却为一直持续到当今时代的中国学术界的伟大的批评运动打下了基础。
汉武帝擅长用拉拢、收买,用任何可以获得完全成功的方法去尽力控制儒学,在这方面,可能没有一个皇帝堪与汉武帝相比。政府的意图是吞食掉儒学,但问题是,究竟谁吞食了谁?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手段来选拔官员、充实政府机构的做法确实能够使朝廷影响很大一部分学者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但也保证了多半官员和皇帝将要接受这些儒家经典的沉重影响。而且,在具有专制性质的政权看来,有些儒家经典明显是危险的书籍。
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后来的其他皇帝,都没有能力把儒学与其早期的作用相分离,这种作用就是:儒学是人民反对暴政的正义斗争的卫士,是一种赞成社会和政治改良(如果不是革命)的力量。作为整体的儒家并没有把他们的良知卖给汉武帝,以换取皇权对这个集群的青睐。其实,汉武帝在世时就受到了儒生的反对。在他死后,尽管历史记载把儒家的凯旋归功于他的在位,但是,大多数儒者对他的评价却很低。 [361] 汉武帝死后15年,他的曾孙汉宣帝宣布了一个计划,想用赞颂汉武帝的卓著功勋来表示对他的怀念,而在他的功勋中就包括了他对儒学的支持和赞助。可是,当时在朝廷任职的著名的儒生夏侯胜——《论语》的一个版本的作者——却批评了这个计划。尽管他知道惩罚是在所难免的,但他还是宣称,汉武帝不应该受到赞誉,因为他是个挥霍者和压迫者,“没有给予人民什么利益”。 [362] 大约与此同时,另一位儒生把汉武帝的做法与孔子的原则进行了对照后说道:“当孔子说‘如果有人要任用我,我就不能建立一个新的东周’的时候,他是要效仿成汤、文、武(所有这些推翻王朝的革命者),立志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根绝残暴和消除邪恶。” [363]
如果皇帝能够使用某种手段控制儒学,那么,儒家学者也确实具有控制皇帝的种种手段。如果这些手段能够更精致一些的话,它们经常会是相当有效的。董仲舒详加说明的手段是最为陈旧的,那就是用《春秋》的原理分析当前的政治事件。它以一种典籍的记载为根据,指出皇帝的左右亲信或者皇帝本人的不足之处,也就是说,如果轻视必要的社会改革,就必定会发生灾变之事。根据《春秋》的类推法,自然灾害被解释为上天赐下的警告,以表示对不公正的政府的不满。
满清政权的第二个皇帝康熙表达了对这种“迷信和无知”思想的忍无可忍。我们不可能不钦佩他的理性作风,也不可能不怀疑这可能是部分地受到了以下事实的促动:儒家学者对他的统治的批评使他很恼火。1699年,康熙皇帝指派了一个由知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要求他们编写一个《春秋》注释的新版本,并务必“消除与‘(《春秋》)经’意不一致的每样东西”。这项工作完成后,皇帝表示很满意。他指出,即使是当年的孔子弟子,对孔子之所述也会有种种不同的传承,那么,几千年之后的儒生又怎么能确定孔子的思想呢?在这个新注释本的序言中,康熙皇帝说,它的编者仅仅是“选择了符合正义的内容”。 [364] 翻开这本书,我们会看到编写者所谴责的“不义”的内容。根据这些内容所述,一个不贤明的和暴虐的君主没有资格得到臣民的忠诚,因而也是可以被赶下台的。 [365]
尽管儒学对政治的影响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时大时小,但这种影响还是普遍性的,并且在总体上讲是倾向于我们所谓的民主政治的。在过去的2000年里,可能没有别的大国能如此继续不断地接受一种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给人民带来福利和满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它就应该受到批评甚至可以被推翻。这一理论明显增强了公众舆论的力量。
孔子坚持的原则是,一个国家应该选择最有才能的人管理政府的日常事务,而选才的基础是他们的德行和所受的教育,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最终产生了科举制度。这个制度是从汉代以来逐渐完善起来的。它的具体做法在各个朝代不尽相同。在清朝,它由三级考试组成,即地方(县、府)、省和国家级的考试,每两年或三年举行一次。在每个级别上,候选人要连续竞争三次才能升级。这种竞争是激烈的,在每次考试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望通过。其间当然也有舞弊现象,但也有防止这种不正当做法的措施。在中国帝王治下的较好时期内,这一制度确实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科举制中最低等级的拥有者(秀才),尽管他可能是穷苦农民的儿子,也拥有很大的社会名望。在某种情形下,他们会得到政府津贴或者担任地方机构中的下级官职,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得到了国家的资助,以完成他们进一步的学业。虽然获得最高级别的人(进士)并不是总能保证被委任做官,但在正常情况下,政府中的大部分重要职位却总是被那些在科举考试中表现突出的人担任。尽管人们也可由其他方式得到官职,但是,至少在许多时期,那些通过了科举考试的人显然最有希望到达官僚等级的顶峰。 [366]
可是,有个重要的例外必须被指出,那就是在由外族入侵者建立的王朝中,统治者自然而然地会把许多最高层的职位留给他们本族的人,无须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的竞争。不过,即使是有了这些特殊情况,中国仍在总体上是被一个深受儒家理想教育浸润过的官僚阶层所统治,并通过在全体人民中的考试选拔来补充新成员。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所有的最高官职都由农夫的儿子来担任。暂时撇开具体运作中的徇私舞弊不谈,一部分官僚贵族的后代有天然的有利方面,比如说他们的家庭有条件提供良好的教育,并且他是在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氛围中长大成人的。所以,有大批的重臣是官僚贵族或各级官员的儿孙,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正令人惊异的是,一些重臣是因为他们的才能而从那些没有上述有利方面的寻常之人的行列中晋升上来的。尽管我们的资料并不完全,但至少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较低的官僚阶层,显然是通过科举考试从大众中汲取了分量可观的新鲜血液。 [367]
至于科举考试的内容,首要的(尽管不是独一无二的)目的是测试应试者所掌握的儒家经典的知识。孔子从未见到这些书中的任何一本,并且肯定会激烈地反对这些内容中的大部分。孔子也会谴责此类仅仅是看重书本知识的考试(例如,见《论语·子路十三》“诵诗三百”章)。一大批生机勃勃的儒家学者谴责了这种考试,但从未取得可观的或最终的效果。
尽管科举考试具有种种缺陷,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却造就了一种具有许多优点的独特的政府。它使这个国家中的许多最有才能的人士在政府供职。就其效果而言,它保证了官员们是有文化素养的人,而不仅仅是获得了社会地位的废物。因为它的真正的基础是儒学的哲学思想和伦理原则,所以,它就给全社会反复灌输一种利害共享的理想,从而产生出一种极其不同凡响的集体精神。尽管它缺乏我们今天所看重的政治民主,但却使普通大众在政府中有了某种代言人,因为在每一代人中,按正常情况来讲,他们的一些成员都会赢得官职。既然教育会自动提高它的拥有者的社会地位,所以,科举制度并未造就一个无阶级社会。但是,这一制度却产生了一个有等级的社会民主体制,而在这样一个如此之大的历史悠久的国度里,可能永远都不会实现完全的社会平等。在这里,尽管仍有某种限制设置了社会的分层,但是,每个农民的儿子在理论上都有希望成为政府中最有权的大臣,而他们中的某一个人也确实不无偶然地达到了这样的地位。
这会使人回想起孔子所坚持的观点:一位大臣应该把忠于原则看得高过忠于君主,而且必须无所畏惧地对君主提出批评。这种观点在御史的职位上得到了机制上的表现。御史的责任就是检查政府中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个人的行为,并且不偏不倚地批评任何人的玩忽职守。这种义务的履行当然会随着御史的正直和勇气程度的高低而发生变化,在某些时代,他们也会被专制皇帝利用为工具。不过,某些御史无疑是怀着最高尚的理想主义而尽到了他们的职责。皇帝确实经常会把一个难以约束的御史流放到边远苦寒之地,或者甚至是处以死刑,但这种做法却不得不甘冒创造一个难以约束的殉道者的危险。
总而言之,诸如此类的事情造就了一个民主制的等级社会,这在一个从理论上讲是绝对专制的君主制社会中是令人惊讶的。然而,这个社会在实际上却远未达到完全的民主政治。孔子为使中国社会走向民主政治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能够为他所建立的原则添砖加瓦的东西太少了,更不用说仅有原则也是不够的。对于有效的民主政治来说,全体人民必须在选择他们的领导人的时候具有实际有效的发言权。这就要求为此目的所创造的特殊的技术手段。但是,这样的技术手段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而这样的成就,最终出现在了世界的另一边,不过,在与这种出现有关的因素中,儒学扮演了一个有益的和意义深远的角色。要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必须得把我们的目光转向欧洲。
第十五章 儒学与西方民主
在西方世界,经过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推动,民主体制以其最快的速度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收获。毫无疑问的是,这些革命并不是被众所周知的启蒙思想的哲学运动“促成”的。但是,启蒙运动的新的思想形态却在令人瞩目的程度上确实决定了人们曾经推动过的革命的方向,而这种革命又给了人们行动的自由。
启蒙哲学与儒学有着一些非常突出的相似性。启蒙哲学发生在17世纪和18世纪期间,而这期间确实是儒学逐渐有效地在欧洲获得其知名度的时期,所以,人们势必要问,中国哲学是否启发了这一时期的某些欧洲思想?对于这个问题,要做出有见地的回答是不容易的。如果一个人对中国特别感兴趣,他就会倾向于强调影响欧洲思想的中国源泉而不甚注意任何别的来源。1940年出版的一本叫作《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的著作对此就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身为作者的一位中国学者在这本书中甚至宣称“中国哲学无疑是法国革命的基本动因”。 [368] 然而,另一些蔑视中国和法国革命的人,却在想方设法地用后者与前者的联系来丢后者的脸。比如说,法国革命后不到40年,麦考利(Macaulay)就曾猛烈攻击了18世纪的“法兰西学院院士”,认为他们相信的有关中国的完整故事“连一个老妈子都欺骗不了,但却被杰出的哲学家认真地确定为政治理论的基础”。 [369] 另一位法国革命的反对者、杰出的法国批评家和社会哲学家费迪南·布伦蒂埃(Ferdinand Brunetiere,1849—1906)则猛烈斥责了他不喜欢的以中国思想为基础的法国民主。布伦蒂埃写道,在法国的教育体制中“除了中国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这场革命制定了这种体制,但它的原理是由‘哲学’确定的,而宣扬这种哲学的那些哲学家则钦佩和称赞中国。一切都是竞争性的考试,不偏向任何东西,尤其是对世袭制不屑一顾!他们的艳羡的灵魂已被满清人的观念勾去了”。 [370]
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法国革命的学者几乎是完全漠视了以下事实:中国思想在法国革命的思想背景中毕竟是起过某种作用的。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被称作是“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最杰出的活权威” [371] 。他在1939年认为,有可能出版这样一部书,在这部书中,论及法国大革命的背景时根本不必提到中国。很自然,他首要看重的是法国自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可是,与此同时,他又警告说:“不要忘记,如果没有那种激励献身的纯粹的理想主义,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精神。” [372] 并且认为,18世纪的法国哲学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这种理想主义的锻造。他写道:
从16到18世纪,哲学家们推出了这样一个人……他摆脱了压制他在人世间升腾的羁绊,哲学家们要求他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天地万物的真正的统治者。这种学说虽然不同于教会的学说,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即认识到人类个人的显著的尊严,并要求对它予以尊重。这是因为,个人具有某种自然而然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而国家机构除了保护这些权利并帮助个人成为有价值的人而外别无目的。 [373]
这种观点可能是正确的,可是,同样真实的是:(1)启蒙运动思想的某些非常重要方面更近似于儒学而不是当时的教会思想。(2)这个事实得到了启蒙运动领袖人物的认可和广泛说明。
在那时,上述启蒙运动与儒学的关系不仅是众所周知的,而且是“臭名远扬”的。据记载,当克里斯丁·沃尔福(Christian Wolff,1679—1754)在一次讲演中认为中国人“靠着治国之术(the Art of Governing)使这个国家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所有别的国家”时,他被勒令在24小时内离开哈雷大学,“否则立即处死”。 [374] 结果是,沃尔福的讲演被远至英格兰的人们热心阅读。许多同样的事情以前是而且将来也会不断地被许多人提起。莱布尼兹(Leibniz,1646—1716)这样写中国人:“即使我们在制造技术上和他们并驾齐驱,或者我们在理论科学方面超过了他们,但是,他们无疑(我几乎羞于承认)在实践哲学方面超过了我们。我的意思是说,依靠这种哲学所建立起来的道德和政治的准则规定了人的行为并且有利于人们的生活。” [375]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认为:“老实说,他们的帝国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它的独特之处是,如果一个省的总督擅离职守并且不被人民拥护时,他就要受到惩处。……4000年前,当我们还不知道如何阅读时,他们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引以为荣的所有基本需要的东西了。” [376] 在英国,尤斯塔斯·巴杰尔(Eustace Budgell)于1731年写道:
所有的作者们在写到中国人时有一个大的共同点是,他们普遍同意中国人完全超过别的民族的是他们的治国之术。甚至是法国人……都不得不率直地承认中国人在治国之术上超过了其他民族,也承认他们从未充分赞美过由伟大的孔子所整理、条理化和加以解说的政治原理。 [377]
当弗朗西斯·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首次建立起他的非常有影响的重农主义学说的政治原理时,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于中国政治进行了详细说明。在他的书中“导论”的后面部分里,魁奈谈到了“与一个已经建成的良好政府相一致的自然原理”,并且认为这样的自然原理只能是“对中国学说的系统说明,而这样的学说值得为所有国家奉为楷模”。 [378]
这些事情之所以有时被忘掉,部分原因存在于儒学向欧洲传播时出现的某些特殊的环境中,以及儒学之声望在欧洲的升降起伏。尽管到过中国的旅行家们讲述中国的故事已经有几个世纪,但他们中的多半人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所以对此也无可奉告。可是,去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却与这些旅行家不同,他们排除万难,凭借无尚的才智,终于在1600年以前获准进入中国。因为这是个有学识的修道会,所以,耶稣会士们就利用他们的学识,在中国的文人圈子中甚至在帝国朝廷之中得到了社会地位。他们作为天文学家(其中一人担任钦天监的重要官职)、御医、外交人员甚至大炮铸造者而服务于中国皇帝。一些人还逐渐成为皇帝亲近的朋友。他们不仅会讲汉语,而且还能用汉语书写。他们也逐渐达到了对于中国社会的更为直接的和本质性的认识,致使后来的许多欧洲学者对他们仰慕不已。 [379] 他们与本会成员以及当时欧洲最著名的人物之间保持着频繁的书信联系。这样的一些信件在欧洲以书籍的形式出版,而另一些则成为有关著述的资料。
这些信件及其有关中国的新信息,在当时的欧洲成为轰动一时的事物。维吉尔·皮诺特(Virgile Pinot)在经过了仔细研究之后总结道,在18世纪的法国,中国“比英格兰更受青睐” [380] ,尽管事实上这一时期正是法国“亲英”的世纪。到了1769年,有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381] 实际上,有文化的西方人对18世纪的中国的了解胜过了对20世纪的中国的了解。不过,既然大部分有关中国情况的信息来自耶稣会士,很自然地就带上了他们之兴趣所向的标记,所以,有许多人坚持认为,从今天来看这些信息,耶稣会士们明显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伪造了他们的对于中国情况的说明。这种非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有名的“礼仪之争”。耶稣会士认为,中国人举行的祭祀祖先和孔子的礼仪并不是偶像崇拜,所以就默认了这种礼仪。别的派别的天主教会士则反对这种立场。所以,耶稣会士们两面不讨好,既未受到教宗的赞许,也未得到满清酋长的青睐。
耶稣会士们确实是只把有关中国的光辉灿烂的图画送到了欧洲。甚至是伏尔泰(他在这一点上为耶稣会士辩护)也承认他们给满清酋长画的像远比这些酋长本人更好看。 [382] 也有人责备说,在描述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时,耶稣会士们没有勾画出它们的真实图画,正如他们在那时对中国的总体理解一样。
【注:这里把中国皇帝改为了满清酋长!】
耶稣会士们在他们的信中以极大的热情向欧洲报告的儒学的确不是17世纪和18世纪在中国普遍流行的儒家正统思想。这种正统思想(一般称作新儒学或宋明儒学)是一种混成的学说。虽然它也体现了许多的孔子思想,但孔子的这些思想却被编织进一个精致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中,而这个哲学体系则吸收了许多佛教的因素。孔子是不会理解这个哲学体系的,并且它在欧洲也不会引起像伏尔泰这样的人的好感。这个被称作“新儒学”的哲学体系对耶稣会传教士们并没有吸引力,因为他们都是一些目光敏锐和具有批评精神的人。况且,他们也有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并认为不再需要其他的。
耶稣会士们越研究这种“新儒家”的著述,越使他们坚信这种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儒学与原初儒学根本不是一回事。作为传教活动之伟大先驱的利玛窦(Matteo Ricci)对宋明儒学的形而上学体系评论道:“在我看来,它模仿了500年前的偶像崇拜(佛教)的学派。” [383] 当他进一步钻研了早期的儒家著述之后,更认为这种新儒学“不是孔子的” [384] 。
利玛窦的观点源自真诚的知识分子的信念。这种信念与传教会士的要求相一致,那就是用这种方法为基督教争取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如他们经常在其他国家所做的一样,中国的耶稣会士全力以赴地使统治集团中的成员改变信仰。这些人主要是儒生。因此,一位当今的耶稣会士断言:“他们的工作势必会开始于切断这种亲密联系。……这种联系使朱子之学(宋明儒学)与孔子的道德哲学合为一体。” [385] 他们精神饱满地着手于这项任务,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功。胡适的研究证实,他们“争取到了那个时代的一些最杰出的严谨的学者” [386] 。这些改变信仰者中的一位(为抛弃了儒学被时人非难)宣称,他根本没有抛弃儒学,而是在天主教中发现的学说确实比“后儒”的“歪曲”更接近于孔子的思想。殷铎泽神父(Father Intorcetta)甚至断言,如果孔子活在17世纪,“他会第一个成为基督徒”。 [387]
耶稣会士对宋明儒学的攻击可能在中国收到了超乎预期的成果。有人说利玛窦是第一个否认宋明儒学代表了古人真实思想的人。无论如何都可以说,当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士开始宣传这个观点时,在中国学者中间还并没有多少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持有这种看法。耶稣会士的观点渐渐变得广为人知,并在中国知识分子圈子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紧接着就有了这种主张,认为宋明儒学并不是原初的儒学,而是对儒学的一种歪曲,因为它吸收了很多佛教思想的内容。这种主张在后来也成为重要的“汉学”学派 [388] 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个学派兴起于利玛窦去世后的几十年间。所以,无论在总体上说,还是就诸如天文学和语言学等具体领域而言,当时的中国文化显然都曾得益于具有科学方法的耶稣会士。这样的受惠尽管是间接的,但也是十分可观的。 [389] 正如胡适指出的,这个“汉学”学派“在过去300年间,为人文和历史研究领域创造了一个科学探索的时代”。 [390] 它也是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其他领袖们的思想背景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391] 因此,尽管17世纪和18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没有成功地使整个中国改信基督教,但正如他们所希求的,使中国文化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所以,从他们的人数很少并且工作条件困难重重的角度去看,这种影响是相当惊人的。
在欧洲,耶稣会士们的活动成为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影响的中介,这同样是值得注意的。耶稣会士送回了详细的并且经常是热情洋溢的对于中国、中国思想特别是孔子思想的说明。他们经常被责难为有意地绘制出了一幅过于光明的中国图画。 [392] 可能他们的一些介绍和说明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人们的这种印象很可能来自以下事实:他们谈论最多的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尽管他们也报告了那时中国的宗教和一些迷信活动,有时还很冗长, [393] 但是,在做这些报告的同时,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讲述那些激起他们热情的事情,特别是出现在诸如《论语》和《孟子》这样的著作中的早期儒学。对于这些经典,利玛窦写道:“当我们仔细审视所有这些著作时,我们没有找到纤微的与理性之光相反的东西,而更多的是与它相一致的地方。这些著作不亚于我们的哲学家的任何东西。” [394]
也有一些耶稣会士们的陈述是对中国的有意贬损甚至诽谤,而欧洲知识界的理解却不是这样。当利玛窦痛惜孔子哲学缺乏超自然因素这一事实时, [395] 他的意图不是说要激起人们对这位圣人的更大兴趣,但最终的效果却是人们对孔子的兴趣大增。
因此,耶稣会士报告给欧洲的绝大部分东西是一种较早的和“较纯”的儒家思想。当然,我们并没有认为他们的努力能在当时中国的孔子哲学重建中大获成功。如果中国后来没有产生大量的批判性的学术成就,比如深入而翔实的考据性研究,这种重建是不可能成功的。在18世纪的欧洲,的确流行着许多关于孔子思想的谬见。不过,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耶稣会士的所作所为已经是相当出色的了。
**所以,阿道夫·赖克韦恩(Adorf Reichwein,1898—1944)写道:“启蒙运动只知道孔子的中国。” [396] 在当时的欧洲,为了尽力斩断形而上的伦理与封建社会的联系纽带,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发现了令他们惊讶的东西,那就是: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孔子以同样的方式思索同样的思想,并进行了同样的战斗。他们在孔子的书中读到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用他的话说明了自己的意思,目的就达到了。’ [397] 这就是说,孔子倡导口头表达的清晰性,亦即逻辑思维的清晰性。因此,孔子就成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守护神”。 [398] 我们只需翻开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就会弄明白这种情形是如何真实。在这本书中,这位法国哲学家有对孔子的一段称颂。他写道:“我全神贯注地读了他的著作,我从中摘录了精华部分。除了最纯洁的道德外,我从未在其中发现任何别的东西,并且没有一丝一毫的假充内行的蒙骗的味道。” [399] 在另外一个地方,伏尔泰写道:“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最值得人们尊敬的时期,那就是人们遵从他(孔子)的法则的时期。” **[400]
可是,保护神的地位是最难维持的。某些耶稣会士和其他热情高涨的人们无疑是做事有些过火,他们夸大了当时的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受到“纯粹”儒学指导的程度。因为种种原因,欧洲的一些人士从一开始对此就持有怀疑的态度,而当中国文化被用来攻击传统的欧洲政治体制时,反攻击也就在所难免了。当莱布尼兹建议中国的饱学之士应该被派到欧洲来教授“自然神学”, [401] 以及伏尔泰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弟子”时, [402] 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就要自然而然地探寻中国人事实上是否真的就是那么讲求道德的。
要想找到负面的证据并不繁难。耶稣会士的敌人,以及那些在中国的经历中不太幸运的商人和不太满意的旅行者,都情愿提供反对耶稣会士的见证。以这种证据为基础,费内隆(Fenelon,1651—1715)在1700年左右撰写的文章中,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自负、迷信、自私和最爱说谎的人” [403] 。而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则在他1748年问世的《论法的精神》中断言:“我们的商人根本没有像传教士们侃侃而谈的那样给予我们关于(中国人的)讲求德行的说明。” [404]
如果传教士们关于中国情况的说明是不可靠的,人们为什么还要相信他们关于孔子思想的阐述呢?因为欧洲收到越来越多的关于中国的部分民众甚至是学者们信仰占卜和魔法的信息,所以,有人就开始怀疑孔子崇高的哲学不是别的,而只是“狡猾的耶稣会士”的发明。后世儒学中的所有附加物和堕落,现在都被归之于孔子本人了,这就是某些人士的最宽容的意见。因此,狄德罗(Diderot,1713—1784)在为《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有关中国哲学的条目中,排列起了一个混杂的队列,并在收尾处对《论语》的内容进行了概括。他说,在这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到,孔子的伦理学远比他的形而上学和他的物理学更为精彩”。 [405] 真实的情况是,狄德罗的文章中只有来自《论语》的一点点东西,致使他的文章内容与孔子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关联,“形而上学和物理学”是后代儒者的著作。但是,只有耶稣会士们才有能力做出这种区分,而狄德罗则在他的文章开头就抱怨说他不再愿意相信他们了。
可是,伏尔泰仍在写着有利于中国的作品,中国仍旧是时尚的。对中国的声望产生决定性打击的是人们丧失了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信任。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它的坚定支持者无疑是对它褒奖过度了。耶稣会士自然而然地对于非常欢迎他们的政府持有乐观的观点。与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相比,他们实际上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描绘成了“完善的和严密的”组织形式,这无疑是相当公正的。 [406] 但是,17世纪和18世纪中国的几个朝代并不是体现其美德的最好的朝代。它们开始于明朝后期的腐败和高压经济,继之以满清的征服,并且让人看到是满人使用特别苛刻的压制政策建立起了他们的统治。乾隆皇帝在位时,伏尔泰把中国称誉为政治宽容的典范,而这位皇帝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以禁止“危险思想”为名的)文献毁坏者之一。 [407]
这些事实渐渐地变得为人周知了。伏尔泰坚决反对像孟德斯鸠那样的批评性的断言,认为中国事实上不是“专制政治”,而仅仅是看起来像而已。 [408] 但是,这种辩解是徒劳无益的。这个国家的另一些斗士大胆地宣称,中国的政府确实是专制政治,但却是最仁慈的和最讲法制的专制政治,所以,这才是最好的政府。在更早一些时候,莱布尼兹以他的中国皇帝是开明专制君主的观点而引人注目。 [409] 当魁奈出版他的论述重农主义政治原理的论文时,他给它取名为“中国的专制政治”。这使人联想起,魁奈是德蓬巴杜夫人(Mme. de Pompadour,1721—1764)和后来的路易十五国王的医生,这无疑会使他认为应该容忍“仁慈的专制政治”。但别人可并不这样认为,并且革命的情绪很快使中国失去了普遍的青睐。
现在让我们来做个扼要的概括。中国哲学由耶稣会士们介绍到欧洲。他们主要是报告或转述了他们认为的最好的东西:孔子个人的哲学和最早的儒学。由于这种哲学在气质上是理性主义的并倾向于民主方向,于是就被欢呼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革命的福音书。可是,不久之后,欧洲人了解到的更多的是儒学的后期形态——宋明儒学,而这种形态的哲学思想部分地是对早期儒学的歪曲,其目的是要为当时的君主权威服务。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曾受到过高度赞扬的中国政府,事实上至少有许多专制政治的特征,而它的一些真正的拥护者实际上正因如此才欢迎它。这就让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孔子和中国政府的美德就等于是耶稣会士的发明,是出于宣传目的的信口开河。与此同时,耶稣会士教团也完全失去了各方面的信任,以至于到了1773年,它被从一个国家驱逐到另一个国家之后,最终被教宗给取缔了。幻想完结了,“中国之梦”结束了。从18世纪末开始,西方世界从未再次对中国感兴趣,也从未对这个国家兴起过那么高的评价。
【注:Pope应该翻译成教宗~,化外夷狄,怎么称皇?】
这个奇妙的各种事件的连锁反应使得许多追寻法国和美国革命背景的人完全不理会这一事实:中国思想的确对于民主哲学的发生和发展做出过贡献。阿兰·哈特斯利(Alan F. Hattersley)在其《民主简史》中认识到了来自“亚洲古代文明国家”的新思想对于“平等、仁慈和博爱”思想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 [410] 可是,总的来说,即使是那些清醒地认识到在18世纪中国对于西方世界曾经产生过影响的人们也并不怎么强调这一点。既然中国被认定为一个专制国家,而孔子又与中国相伴随,那么,人们就会想当然地认为,孔子的思想很难对民主的成长做出贡献。
居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被称作“缔造了法兰西的科学和文学史” [411] 的人,他对于法国革命的文化背景进行过详尽分析。尽管他不否认外在影响做出过一定的贡献,但他还是做出结论说,革命的哲学基本是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是长期处在法兰西思维方式之下的思想进展的结果,并受到了这个国家当时的社会状况的激发。朗松点出了在1700年左右出版的三本法文书籍,并接着说:“这场运动开始于18世纪的政治哲学和革命学说。”其中的一本书是费内隆的Telemaque。 [412]
把费内隆作为革命先驱者,非常便于进行我们现在的探究。因为碰巧在他的《死者的对话》(朗松也引用这本书来表达同样的观点 [413] )中,费内隆激烈地攻击了孔子哲学。所以,从这本书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在18世纪初叶,法国知识分子所认为的被歪曲了的孔子哲学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将费内隆的观点与费内隆所理解的孔子的观点作一比较,从而显而易见地看到孔子的观点更靠近这场革命的哲学思想。这本书出版于1700年 [414] ,其内容就是费内隆所设想的苏格拉底与孔子之间的一场对话。费内隆的心思让读者一看便知。他露骨地诅咒中国人。很清楚,费内隆是通过苏格拉底而发言的。
苏格拉底一开始就否认了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他与孔子之间的相似性。苏氏宣称:“我从未想过让人民成为哲学家。……我将那些粗俗的和自甘堕落的人斥之于千里之外,限制自己只教诲一小部分有培养前途的弟子。”
孔子有礼貌地回答说:“对我来说,我避免做出难以捉摸的逻辑推论,而是把自己的思想限定在具体的人的道德实践中。”苏氏接着说:“我认为,如果不先去从逻辑上证明本体论的原理,人们是不能建立起真正的道德准则的……”
孔子问道:“但是,你能用这些个本体论原理防止你的弟子之间出现的思想分歧和争论吗?”“不能。”苏格拉底告诉孔子,并且表示正是此一事实使他失去了对人类的希望。因为,作为个人,我们对于人类中的大多数是无可奈何的。他认为:“通过榜样和论辩,慢慢灌输以最伟大的艺术,也只能影响非常小的一部分人,而这部分人生来就比别人好。所以,在我看来,对一个国家进行总体性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对人类的幻想破灭了。”
孔子则答道:“对我来说,我写下的和传给弟子的思想,是力图让道德原则在我们帝国的所有地方流行起来。”对此,苏氏的意见是:孔子,你作为“皇室成员,在你的国家有巨大的权威,你能够做到的许多事情,像我这样的一个工匠的儿子却是无法做成的”。苏氏接着就在一段长篇讲话中扩展了自己的观点:总的来说,人民应该把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良好的领导阶层。“从哲学上讲,(人民)要遵从美和善,而这种美和善仅仅来自于信念,来自于对美和善的真实而自由的热爱。但是,这种精神修养从来都不可能在全体人民中加以普及,它保留给了某些经过挑选的领袖人物,他们天生就与其他人有分别。总而言之,在风俗习惯和思想观点方面,人民只能够具体实践某种美德,而这些美德的标准则是那些有自信心和有权威的人们所制定的”。在这场对话的剩余部分里,苏氏通过详细的论述,认为中国人并不(像他们曾经被描述的那样)是个古老而又令人钦佩的民族。
朗松就已认识到,如果说费内隆(亦即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是一位革命的先驱者,他的思想显然距离“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情感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相反,正是费内隆所认为的孔子哲学反倒更接近于这些情感。事实上,这些情感与孔子的思想风格是亲密无间的。
朗松在两篇文章中发展了他的如下论点:作为法国革命基础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和政治原理基本是土生土长的。首先,尽管承认外部(包括来自中国)的影响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力主“这场引发18世纪法国理性主义的运动……是内在辛劳的结果,这种辛劳开始于文艺复兴,随后转化为法兰西社会的精神,并在17世纪末叶突然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和更加灵敏快捷”。
因此他认为,在1680—1715年间发生的思想转变具有以下显著特点:(1)要求人们具备清晰的和有条理的思想,关注事实和经验,不向偏见和权威让步;一个人必须为他自己寻求真理。(2)良心是自主的,信条是独立的,因此,所有地方的善人从根本上讲都有同样的道德原则,这种原则与种族或宗教无关,而且,个人可以自己判断善与恶。总的来说,“善”就是“金科玉律”,就是一切事物都应该达到的标准。(3)善良和快乐是一致的。人们不应该设法消除人的欲望,而是要对它加以引导。人生的重点在于此世的享乐,所以,来世的赏罚就消失了。(4)“善”并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文化和文明的产物。但是,卢梭(Rousseau)在后来却持有与此相反的观点。(5)快乐的哲学被扩展到了互惠的地步,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使他自己幸福,就需要使别人幸福。(6)“人道”的美德代替了“仁慈”的美德。 [415]
朗松承认,有关中国的新知识对于上述第二种思想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对于以上所有思想,他都力图寻找本土的发生和逻辑的说明。在某种情形下,这种做法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例如,从自我主义到利他主义的转化,事实上并不像他在此描绘得那样简单和必不可免。 [416]
有两个事实显然值得指明。首先,正如读者也会发现的,在上述18世纪6种法国思想中,每一种最终达到的地步都与《论语》和真正早期儒学中的孔子思想之间具有不同寻常的相似性。其次,1680年到1715年之间,亦即朗松规定的这种思想转化期间,正是这种早期儒学被有效地介绍给法国公众的时期。一些早期儒家著作的最早译本就在1662年出版,而其他的则陆续在随后的十几年间问世。 [417] 在1685年,一个颇有学识的特殊的法国耶稣会教团被路易十四国王派往中国,他们还携带着国王的信件。从那时起,他们以及追随他们的其他人便与欧洲的一些最著名的人物进行了大量的通信往来。这些信件构成随后十几年间出版的一些书籍的基础,这使得中国(以及孔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名度。 [418]
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中,朗松讲道:“1692年到1723年之间,法国社会的上流阶层被唤起了社会良知和改革精神。这些都是闻所未闻的。”朗松还力图显示出,不要“妄想低估外来的(亦即英国和美国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将因法国当时的形势发展扩大其作用范围。尽管朗松的主张有其长处,但他有时所引述的原因却不适宜于说明相关的结果。路易十四在位的后几年的压迫性政策激发了“一种改革精神,为公众福利而积极奋起的精神”的传播,这是毋庸置疑的。 [419] 但从某种程度上讲,起到这种激发作用的因素不止这一点。而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会有这种特殊的精神?显而易见,它并不总是由压迫人民这一简单事实所唤起。在法国或在其他地方都是如此。
我们更不可能接受的是这种说法:“平等的原则逐渐形成了,但它源自何处呢?显然源自于对不平等的和压迫性的人头税的关切。” [420] 这无疑是一个原因。但真正的原因是对不平等待遇的抗议,其中包含的是:人们认为自己有资格享受平等待遇,亦即认为人们相互之间是平等的。所以,促进平等精神之产生的真正的原因很可能远比朗松所说的更为复杂。在促进向这个方面发展的力量中,有来自宗教改革的,也有来自英国的,还有来自中国的影响。当时的西方人相信,使他们最感震惊的人类生来平等的思想在那时的中国是很普及的。这个惊人的事实被报告给欧洲的时间是在1692年前的100年,而1692年正是朗松所确定的唤起法国社会良知的时间。 [421]
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德国、英国和法国,有大量的学者、哲学家和政治家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要列举他们的名字就将超出本书的范围,况且这项工作已经有人做过了。 [422] 我们也不能详尽考察存在于以下双方之间的每个相似性:一方是18世纪西方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另一方是早期儒学。这种比较可以轻而易举地塞满一本书。莱布尼兹和沃尔福都认识到,在欧洲相当重要的自然法的概念,非常类似于儒家的“道”的概念。 [423] 有人认为,正是在此基础上,蒂尔戈(Turgot,1727—1781)这位对中国有着浓厚兴趣的路易十六国王的大臣,建议他尊贵的主人对法国君主政体的运作做出某种程度的改进。 [424] 18世纪的法国和中国也有以下的共同思想,即认为政府的正当目标是人民的幸福, [425] 而治理国家应该是一项协作性的而不是竞争性的事业,甚至孟德斯鸠在上述后一点上也称赞了中国政府,他评论道:“这个帝国建成了家庭式的政府。” [426]
既然不便为上述的所有观点都提供出必要的证据,那么,就让我们只考虑作为法国革命基础的两项原则:第一,革命权力;第二,人的平等。
革命的法国国民议会宣称:“当政府侵害人民的权利时,对于全体人民,以及对于人民的每一部分来说,起义造反就是最神圣的权利和最不可推卸的责任。” [427] 尽管这个主张与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理论完全不同,但当然也不是欧洲人第一次向旧观念发出的挑战。这种观念的提出一定是受到了中国人所发明的政治理论的意味深长的加强。因为在中国——它被当时的欧洲人广泛地认为是治理得最好和最有秩序的国家——有一个原则是:面对统治者的压迫,人民的革命行动肯定是“最神圣的权利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这项原则早已被接受为一条箴言,它含蓄地表达在《论语》中而明确表达在《孟子》中。 [428] 在中国,对暴君的最经常的威慑就是爆发革命的危险,这一事实早就被传教士们报告过,并在大革命的很久之前就被一些欧洲著作者,比如路易十五宫廷中的魁奈和英国的奥立佛·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730—1774)等人说到过。 [429] 孟德斯鸠则写道:“中国的皇帝……据说如果他的帝国统治不公正,他将失去他的帝国和他的性命。” [430]
平等原则的情形也很有意思。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正式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它的第一条宣称:“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所以,公民的等级差别只能建立在从事公共事业的基础上。”这些话语与美国独立宣言之绪言的相似性经常被人们指出。但是,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在1696年的早些时候,一本由耶稣会士李明(Le Comte,1655—1728)撰写的著作就已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他写道,在中国“贵族从来都不是世袭的,人们的本性也没有任何差别。有差别的是他们通过后天努力所获得的社会地位”。 [431]
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J. Laski,1893—1950)写道:“法国大革命对民主理论做出的贡献是它坚持认为这项事业必须向有才能的人开放,这就是说,无论这场革命有什么样的局限性,它毕竟是对妨碍到达平等之路的出身或种族或宗教等等的否定。” [432] 可是,关于这一理论贡献的来源,却让人颇费思量。在革命发生的很久之前,就有一种思想在欧洲广泛传播。这种思想认为,中国人就是直接根据人的才能来任命官员的。维吉尔·皮诺特指出:“赞美中国的人们相信,他们发现了这样一个地方,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那是一个国家;在那里,一个人靠着良好的品质就可以获得国家的高官显位;在那里,每个人都是根据他们的道德品质来排列其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即使有王公的青睐和高贵的出身,也不能虚妄地任命一个既无德行又无学识的人做官。然而,这种事情在欧洲是罕见的,或者甚至就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传教士们无论其国籍如何,都用狂热的词句赞美这个令人称奇的中国的等级制度,因为这个制度的基础不是别的,只是个人的良好品质。” [433]
传教士的这种内容的报告早在1602年就有了, [434] 并且不间断地持续着。在1735年出版的一本受到广泛阅读的著作中,杜霍尔德(Du Halde,1674—1743)认为,在中国,“一位学者,即使是农夫之子,也如同豪门子弟一样,很有希望达到总督的高位,甚至还能做宰相”。 [435]
这些评论激发起了欧洲人广泛的兴趣。许多书中都讨论了这些问题,其中包括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1577—1640)于1621年出版的《沉思的分析》。 [436] 另一个名叫尤斯塔斯·巴杰尔(Eistace Bidgll,1650—1711,曾是《闲谈者》和《旁观者》杂志的撰稿人)的英国人在1731年提出,英国应当采纳中国人的做法。巴杰尔写道,他考虑了这样一项准则,“共和国的每一个有荣誉的或者有报酬的职位,都应该作为对真正的良好品质的奖赏。如果现代政治家不把它记在脑海里,这个准则(它本身是极好的)就不能在像大不列颠这样的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王国里被遵循。我奉告这样的政治家,就是在这个时代,这个光辉的准则受到这样一个国家最严格的遵奉。这是个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多、治理得最好的国家:我指的是中国。……在中国,如果一个人不是个真正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就不能成为一名官吏,亦即一位君子或者有能力胜任政府的任何职位的人”。 [437] 在1762年,奥里佛·戈德史密斯就以这个观点作基础,猛烈攻击了大不列颠王国的世袭贵族制。 [438]
在法国,一些作者也陈述了这一观点,这些作者包括伏尔泰、在1759年成为法国财政部部长的艾蒂安·德·西卢埃特(Etienne de Silhouette,1709—1767)、在1774年到1776年间担任同一官职的蒂尔戈、钦差大臣皮埃尔·波伊沃里(Pierre Poivre,1719—1786),以及创立重农主义学说的魁奈。 [439] 简而言之,就是在法国大革命“对民主理论做出贡献”——其原理是:人们应该纯粹根据个人的品质和成就被选做官——的时候,至少在中国政治中,这种理论成为常识已有好久了。
那么,难道我们是要下结论说,中国的新知识是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吗?当然不是。导致革命发生的原因很多,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只是这里不是尽述其详的地方。我们关切的不是上述这些方面的革命,而是精神领域的革命。在17世纪和18世纪,这种精神革命使得整个西方世界的思想逐渐地再次朝向了东方,走向了民主。不用说,儒学的新知识只是这场精神革命所依靠的许多因素中的一项。
可是,正是这一因素,其重要性既没有被适当地认知,也没有被有效地考究过。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17世纪和18世纪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不论是转变,还是相似性,都不是肤浅的、表面化的。显而易见,这些相似性部分地显然是由于巧合,但不可能全部都是这样。要决定在什么程度上它们是一种文化影响另一种文化的结果,将需要悉心的探究,而这种探究尚未达到充分有效的程度。我们深信,当它达到这种程度时,一段崭新的和意义深远的篇章就可以增补到民主思想的变迁史中去了。
有迹象表明,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取得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该文发表于1948年,作者是论卫励(Arthur O. Lovejoy,1873—1962),标题是“浪漫主义的中国之源”。它是一项以事实材料为根据的细致入微的研究,研究的目标是,在一个单独的领域——美学,18世纪的中国对一个单独的西方国家——英国,所产生的影响。论卫励总结道,从中国引进了“一项新的审美规则”,他说:“当规律性、简易性、一致性和简便的逻辑可解性的思想首次受到公开指责时,当真实的美是‘几何图形’这一设定不再是‘如自然规律一样得到全部赞成’的东西时,现代审美史就到了它的转折点上了。在几乎是整个18世纪的英国,对这个设定的反对一般认为起初是由于中国艺术的影响和典范作用所致。” [440]
中国思想的这一作用在艺术之外的其他领域也产生了反响。所以,中国思想表现为一种代替物,代替的是用以保护欧洲思想的一项已被确立的公理,而此公理显然被认为是受到了全体文明人的赞同。它与诸如人类幸福的价值这样的基本问题有关。吉尔伯特·钦纳德(Gilbert Chinard,1881—1972)指出:“整个基督教文明建构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在这个充满眼泪和苦难的现实世界中,幸福是既没有希望得到的又是不可能得到的。” [441] 当然,反对此观点的人也很多,但总的来说他们是孤零零的声音,或者是微不足道的小集群。
所以,正是在东方的发现才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正如伏尔泰所生动说明的,它是“一种新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宇宙”。他们发现当时的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并且(无疑是有根有据的)也是繁荣兴旺的。 [442] 她在平静的自足之中也受到一些原则的约束,而这些原则在许多方面与欧洲流行的相反。在这个国度里,幸福不是令人皱眉的东西,而恰恰被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不仅是个人的,甚至也是国家的目的。人类平等并没有被否定,相反,那些报告中国情况的人认为,它是社会和政治理论的真正基础。
【注:直到启蒙运动时中国还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可见之后的商博良之流确实做了不少见不得人的事情。】
在欧洲,这个“新宇宙”正好投合了受到异端国家支持的那些不合乎传统规范者的心意。再也没有人会说任何与欧洲传统相冲突的做法是“不会起作用”或“一事无成”的了。 [443] 伏尔泰高兴地断言:“同样一个人,既坚持认为——与贝尔(Bayle,1647—1706)的观点相反 [444] ——一个无神论者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同时又断言世界上的一个最古老的政府(即中国政府)领导的是一个无神论者的社会。” [445] 社会现状的辩护者宣称,仅仅以良好品质为基础而任命官职,却并不在乎被任命者有没有世袭地位,这样的准则是对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破坏。然而,巴杰尔的回答是:“这个光辉的准则受到这样一个国家的最严格的遵奉,这是个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多、治理得最好的国家,我指的是中国。” [446]
如果欧洲人的旧标准不被推翻,传统的辩护者就不得不遭遇类似中国思想这样的威胁。事实上,他们最终遇到了。然而,他们接着就在暗中彻底破坏了中国和儒家思想在欧洲的声誉。结果是,自从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以来,西方人完全忘记了古代中国对于西方民主思想的发展做出过的意义极其深远的贡献。
在欧洲人刚刚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时候,莱布尼兹表示,他很希望出现一种“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明的相互交流”。 [447] 尽管这种全面的交流在当时不太可能发生,然而,局部的但却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价值渗透却很可能是发生了,并且比我们认识到的范围更大、程度更深。
如果说欧洲人尚且没有觉察到中国思想对于他们的民主传统的影响程度,那么,大多数美国人很可能更加难以觉察到18世纪欧洲的启蒙哲学(特别是法国哲学)对于美国民主思想和机制之发展的影响。人们之所以会轻易忘掉这一点是由于以下事实:美国革命先于法国革命,并促进了法国革命的发生。
然而,法国启蒙思想在美国革命的酝酿阶段却发挥过明显的作用,并对于革命之后的美国民主思想的发展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被称作是“美国启蒙运动的象征”。 [448] 孔子哲学对美国民主思想之发展的影响主要地并且只可能是通过这种法国影响而表现出来。在他们的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那些美国人对中国了无兴趣。这种状况可以部分地由以下事实做出解释:就在美、法两国在文化上关系最为密切的时候,中国在欧洲已经是信誉扫地了。
可是,至少有一条明晰的联系线索贯穿在魁奈的重农主义学说之中。人们有时会有疑问,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两人产生过重要影响 [449] 的重农主义理论是否真的在深远的程度上导源于中国。 [450] 魁奈说过,他的学说得之于中国,这种观点当然是可以商榷的,但是,每一个熟悉那些讲述中国政治和经济理论之文献的人在读魁奈的著作时,都会感受到中国思想与魁奈主张之间的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冲击。进而言之,魁奈所说的许多观点相当明显地是出自像耶稣会士和伏尔泰这样的作者所写的有关中国的陈述中。 [451] 刘易斯·马弗里克(Lewis A. Maverick)认为,魁奈的《中国专制政治》(首先阐述了重农主义的政治方面)的前面7章“全部抄袭”自一本描述中国的书,这本书的作者乃是雅克·菲利伯特·鲁斯洛·德瑟吉(Jacques Philibert Rousselot de Surgy,1737—?)。 [452]
重农主义特别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并力主国家应该倡导之。重农主义者同时认为,贸易和工业不是生产性的。他们倡导自由贸易,主张只对农业课税。魁奈认为,政府应该由一个具有“专制”权力的君主来领导,但是,他的统治不应该是“苛刻而残暴的”,而是要像中国的皇帝那样。 [453]
因此,在魁奈的理论中并非找不到以中国文献为基础的地方。当然,魁奈和他的学派中的其他成员无疑是要使中国帝王专制权力的思想(正如我们所见,这是对孔子思想的歪曲)适应他们欧洲人的“开明专制主义”的理论。进而言之,他们以一种缺乏甚至不符合孔子理论的方式强调了私人财产的重要性和“节俭起家的……富有业主”的作用,“以便让他们担任最受尊敬的公职”。 [454]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在1767年到了法国,而魁奈的《中国的专制政治》正是在这一年出版。事实上,富兰克林订阅并投稿的那个杂志社发行了这本书的第一版。 [455] 在魁奈家中,“富兰克林找到了他最感兴趣的东西:一个快乐的、亲密的、有学问的和哲学的社交场所”。 [456] 富兰克林也成为两位最有影响力的重农主义者米拉博(Mirabeau,1715—1789)侯爵和蒂尔戈(Turgot)的朋友。因此,正如伯纳德·费伊(Bernard Fay,1893—?)所说,富兰克林“把这个著名学派的巨大影响为美国所用,这是走向掌握(法国)舆论的一大步骤”。 [457]
富兰克林也直接从重农主义学者那里借用了一些思想。费伊写道:“他把它们简化为最简明的因素,明白了如何在英美关系的讨论中使用它们,以及在支持美国农民反对英国商人的要求中让它们发挥什么作用。……这是他的心灵深处的一场真正的革命。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1652—1722)的古老的英国辉格党体系,以及威廉·彼得(William Petty,1623—1687)的重商主义理论,这些个1720年以来一直指导着他的理论体系,突然之间就过时了。英、美之间关于政治体制的讨论早已使他厌烦,他认为这错过了主要问题……重农主义给他装备了一种学说,在那些个暴风骤雨的年代里,他把这种学说使用在了他的著述之中。” [458]
杰弗逊也对重农主义学者的思想极其感兴趣,并且受到了他们的明显影响, [459] 尽管他并不接受仁慈专制的观念。 [460] 杰弗逊的一封信明显地表现出他意识到了重农主义与中国之间的联系。 [461] 但是,无论是杰弗逊还是富兰克林,都未曾受到促动,去对中国哲学本身做过任何值得注意的探究。
尽管这种影响无疑只是在间接意义上的,但是,把托马斯·杰弗逊的思想与孔子思想作一番比较还是很有趣的。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形而上学的不能容忍,在于对穷人的关切和对富人的反感,在于对基本的人类平等的坚持,在于对全体人民(包括奴隶在内)的最起码的尊重,以及在于不是对权威而是对“每个诚实的人的头脑和心灵” [462] 的召唤。杰弗逊的表述是,“整个治国之术由真诚的做人之道所组成”,这惊人地类似于《论语·颜渊十二》“季康子问政”章,以及其他我们引用过的一些诸如此类的例子。 [463]
【按:孔子显然没有对富人有什么反感,只是希望富人能”好礼“,就像子贡那样!认为孔子也反感富人确实不合适。】
尽管他们都是普通人之事业的强健斗士,但是,无论是孔子还是杰弗逊(正如一些民主倡导者之明显所为一样)都没有小看了此事实:人们在实际才能上并不是平等划一的。1813年,杰弗逊写信给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人们之中是有一种天生的贵族,其基础是德行和才能。……也有一种人为的贵族,它建立在财富和出身之上。……我把天生的贵族看作是大自然的最精致的礼物,理应让他们去负责教化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工作。……我们甚至不是可以这样说吗?为了建立最好的政府,就要最有效地为那些经过公正挑选的天生贵族提供政府职位。” [464]
要想更简明快捷地实施中国科举取仕式的制度将是困难的。杰弗逊认为,应该把国家里有才能的年轻人挑选出来进行教育,以使他们担负起治国的重任,这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所以,他在1779年向弗吉尼亚众议院提交了一项旨在将此目的化为具体措施的议案,这就是“进一步普及知识”的A议案。这个议案宣称,对民主的最好护卫就是普及教育。它也断言,政府应该由“精明和坦诚”之人管理,并且正是“这些人,他们本性中禀赋有天才和德行,再加之以他们理当得到的自由教育的润饰,使他们能够捍卫他们的同胞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神圣宝藏,所以,他们应该被委以重任,而这种委任与他们的财产、出身或其他偶然的条件或境况全然无关”。可是,既然穷人无力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教育资金,那么,为了公共利益,他们中的有才能者“应该被挑选出来并予以公费教育”。
杰弗逊的议案力图建立一套具有三个层次的教育体系。在地方学校里,所有的孩子将接受三年的免费教育。“学校中的那些最有天分的孩子,因为家长太穷而无力供养他们进行深造”,所以,要定期地通过“最认真和公正的考试和考查”的挑选之后,把他们送往20所初中的其中一所,接受“公费”教育。在那里,学生们要接受经常不断的考试,以便只留下最好的。最后,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将被送往威廉—玛丽学院(William and Mary College),继续学习三年他们选定的学科”。杰弗逊解释道:“根据我的这个规定在贫穷阶层中选择年轻天才的计划的作用,我们希望会有益于这个人才(在本质上公正地散布在穷人和富人之中)辈出的国度。但是,如果不寻找出来加以培养的话,他们就会白白地消亡掉。” [465]
杰弗逊的计划有三项原则与中国的科举制度是相通的:(1)把教育看作是国家的首要关切。(2)才能非凡的学生,将通过竞争性的考试,在三个层次上进行挑选;在最低层次上,学生将在一个小地区内挑选,而最高层次的挑选将是全国性的(与中国的县、省和全国会考即乡试、省试和会试相一致)。(3)主要目的是“有益于国家”挑选公务员,也就是说,国家机构中的官员都应该是其公民中的最有才能者,而无关乎他们是富是穷以及门第如何。它与科举制度不同的是为所有的人提供某种程度的免费教育,并要求对有才能者实行全部公费教育。对于他的“天生贵族”,杰弗逊不仅要求他们必须通过考试,并且还要通过竞选而得到政治地位,而不是像中国那样完全依靠任命。 [466]
当然,这些相似性还不能证明杰弗逊的治国思想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可是,却有一种受到这种影响的明显的可能性。可以肯定,杰弗逊在1779年提出这个议案之前就知道中国科举制的存在。有证据表明,不晚于1776年,杰弗逊就读过(并且还做了大量的笔记)伏尔泰的一本书,该书宣称,“一个人的心灵不能再想象出一个”比17世纪初的中国政府“更好的政府”,在那里,所有权力最终掌握在“只有通过几次严格的考试之后才得到任命的那些”士大夫手中。 [467] 中国的科举制度在大批早期的欧洲书籍中有过详尽的描述, [468] 其中至少有一本是在杰弗逊的图书馆中。 [469]
杰弗逊认为,他的教育计划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性。他坚信,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加强民主体制本身,使其不至于慢慢地堕落为暴政。 [470] 但是,他的1779年的A议案被作了大量修正,从而破坏了它的目的。1806年,身为总统的杰弗逊向国会提议,应该对宪法加以修正,以便于能够建立一种“国家教育制度”。 [471] 他在1813年写信给约翰·亚当斯,说他仍希望他原初的A提案的原理可以作为“我们政府的这座大厦的栋梁” [472] 。到了1817年,他又写道,他“现在全身心地专注”于推进一项教育计划,此计划是他将当初的A提案加以具体化。 [473] 他为了这项计划而继续不断地工作和写作,直到他最后的岁月。 [474]
尽管杰弗逊所倡导的教育体制未被采纳,但是,它的原理——根据人的才能而不是名望来挑选官员——却被西方的各个民主政府所接受,也就是说在它们的行政机构中通过文官考试制度来招收新成员。关于这个体制在大英帝国的起源,我们不必再去推测了。在1943年,邓嗣禹发表了一项认真的根据文献进行的研究,显示出英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受到了中国科举制的启发。根据另外的证据,邓氏证明了这种考试率先被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采用。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建立的机构与中国有联系。**当英国上院对于是否采用这种体制而进行辩论时,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样参照了中国的体制。 **[475]
主要是在英国的影响下,美利坚合众国最终采用了文官考试制度。可是,值得指出的是,此方法在议会尚未通过之前,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就评论道,在“要求公共职位的候选人首先通过考试”来显示他们的素质方面,“中国领先于我们,英国和法国也领先于我们,并对这种不够严密的做法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正”。 [476]
【按:美国第20位总统加菲尔德应该政党内部分赃不均被枪杀了,这才是美国使用文官考试制度的直接起因!】
第十六章 孔子与中华民国
有一种观点认为,就在他自己的时代,孔子就是政治保守主义者,还对君主专制主义给予了强劲的支持。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进而认为,儒学主要是专制帝王为了迫使其臣民的服从而使用的宣传工具。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之下,孔子的名字当然会在中华民国的某些集群中备受诅咒。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20世纪的前50年中,孔子的名字确实经常被某些军阀和其他一些人(至多也只是民主政治的可疑朋友)所利用,这对孔子的声誉有损无益。因而,在孔子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中,人们对于负面东西的印象在日渐加深;这样一来,中国革命的进程也就成为传统儒学被引进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取而代之的过程。对于这样的结局,我们并不难理解。
如果儒学被局限为仅仅是一种受到清王朝保护的僵硬的国家正统思想的话,以上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通过我们的研究,却发现与后世的正统儒家思想相比,孔子本人的哲学是相当不同的东西。在上几个世纪里,满清帝国之内兴起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由许多相当有才能的和具有独立性的学者发起,其目的是力图复兴早期的儒学。在上一章中我们就已看到,由耶稣会士带到欧洲的早期儒家思想对西方民主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事实上,儒家思想在中华民国的建立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
显而易见,并不是仅靠儒学自身就产生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西方的压力,这种压力明显证明,中国不能继续在他当时的道路上走下去,也不能继续保持专制政治了。但是,对于民国政体的形式,以及可能还对于中国完全变成一个共和国的事实,儒学确实是有所作为的。西方对日本的压力使这个国家在1868年深刻改变了他的政体,但日本人并未实行共和制,而是建立了牢固的中央集权君主立宪制。日本和中国对于基本相同的刺激的不同回应主要是由于他们的不同的传统哲学所决定的。
纵然20世纪的许多中国人并不能把正统的国家儒学与被歪曲了的早期儒家思想区分开来,也不意味着所有中国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胡适就指出,这种近代的儒家正统思想“没有把握住古典儒学的民主精神”。 [477] 不过,最重要的却是以下事实:作为“中华民国之父”的孙中山(逸仙)则完全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对孙中山哲学背景的分析中,罗纳德·许仕廉这位中国外交部的一位前任官员写道:“清代的考据运动也对孙博士的思想有极大的影响。……大约250年前,一群学者开始倡导思想解放和文献考据。一些人甚至否定除了《论语》的原初部分之外的全部儒家经典的权威性。……他们想回到孔子。依照戴季陶(孙氏的革命同事)这位公认的孙逸仙主义权威的说法,孙博士常常自认为是哲学上的儒家学派的现代继承者。” [488]
在孙氏的讲演中(这些讲演印行之后发行量很大,并且极有影响),他一再把孔子欢呼为民主主义者。他断言:“孔子和孟子都是民主的倡导者。……孔子总是引用尧、舜之语,因为他们不把帝国据为自己的世袭财产。虽然他们在政府名义上是君主专制的,但事实上却是民主的,而这就是孔子为什么要赞誉他们的原因所在。” [489]
尽管孙中山认识到他从西方借用了很多东西,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只是个西方民主的引进者。事实上他宣称:“中国领先于欧洲和美洲几千年就发展出了一种民主哲学。” [480] 并且再次断言:“欧洲超过中国的,不在于政治哲学,而只在于物质文明。……我们需要向欧洲学习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哲学。因为在真正的政治哲学原理方面,欧洲还需要向中国学习。” [481]
在孙中山的被称作《三民主义》的著名著作中,孙氏宣称,如果中国要想恢复它在世界上的正当地位,其根本之处就是“复兴我们古代的道德”。然后,他列举了被称作儒者的那些人通常所必备的美德。但是,他更令人惊讶地断言,同样必要的是复兴中国古代的学问。接着,他从儒家学派的经典之一——《大学》中引用了一节,用以说明这种古代政治哲学必须被作为“国宝”来捍卫,因为这种东西是外邦不曾拥有的。 [482]
孙中山之所以做出如此表述的原因之一,无疑是想让中国人重新获得自信。但是,如果把它们解释为除了空洞的爱国主义的姿态之外一无所有,或者认为他并没有受到中国哲学的深刻影响,那将是大错特错的。保罗·莱茵伯格认为,孙氏的思想“形式上是西方的,但内容仍是中国的”。 [483] 这是确凿无疑的,其证据甚至可以来自对他的言论的不太经心的研究。众所周知,孙氏受到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影响,但当马克思的思想和儒学相抵触时,马克思有时会是失败者。
这一点在有关阶级斗争的学说上表现得很清楚。孙中山指出,自从马克思创立了阶级斗争学说后的好多年以来,人类社会在经济公正方面发生了非常令人可观的进步。他问道:“什么是社会进步的原因呢?如果我们以马克思学说为基础而进行判断,我们一定得说这种原因就是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则是起因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而且,因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互相对立、不能调和的,所以,阶级斗争就成为最终结果,而斗争的结果也就是社会进步。”可是,实际情形已经证明这不是事实。其实,对工人的较好待遇意味着资本的更大利润,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提高工人的薪金。“因此,资本家和劳工的利益被证明不是冲突的,而是一致的。而社会进步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在总体上的经济利益的一致,而不是冲突”。所以,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步的原因,而是标志着社会进步中的灾难。孙氏总结道:“我们不应该称马克思为社会生理学家,而应称之为社会病理学家。” [484] 在此,孙氏所受的影响显然是中国的,而且是儒家的,它强调的是社会所有成员进行协作的必要性。同样的影响也表现在孙中山对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否定之中。 [485]
民国政府的政体所依据的,不是我们在西方民主体制中所熟知的三权分立,而是孙中山所制定的五权分立。阿瑟·霍尔库姆(Arthur N. Holcombe)在写到孙氏所制定的整个中国政治体制的计划时说:“不管你认为孙博士的体制是多么的琐细,他的计划的基础是一种堪与任何其他现代革命领袖的思想相提并论的政治哲学。” [486] 孙氏自己很清楚,这个计划的基础是中西思想的融合,是得益于孟德斯鸠和孔子哲学的。 [487] 他有一次甚至说,他的五权分立体制的计划基本上是中国帝国政体的翻版。 [488]
在研究历史上的种种民主政体的结构及其实施之道时,孙中山断定它们缺乏两种功能。他进而断言,那些民主政体所缺乏的功能恰恰表现在中国帝政之中,因为在这种帝政中,一方面是有儒家思想辅助,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官员们获得了很大程度的不受皇帝干涉的独立性。孙氏对于这样的结果大加夸赞,所以就把这两项功能规定为两种独立的权力,归属于五院中的两院。 [489]
【注:无独有偶,美国总统威尔逊也曾在《国会政体》中讲述美国不是三权分立而是议会权力大于其他两权。】
这使人想起孔子所强调的一个大臣的责任:批评其君主所犯的错误。在帝制下,这项责任逐渐发展完善,最终专属于一些特殊的官员(御史)。这种官员有责任找出并谴责政府中任何地方的腐败堕落。尽管孙氏认识到了西方政体中的立法机关和法院的批评功能,但他还是认为政府中有这样的一个由政界元老组成的专门机构是很有好处的,这些元老的确定职能是不偏不倚地进行批评,并弹劾那些腐化了的官员。所以,他在他的五权分立的体制中建立了一个监察院。 [490]
作为孙氏的第五权之基础的科举制度并不是孔子制定的。可是,这个基础明显是孔子打下的,因为孔子一再认为有必要“举直”,有必要把政府的行政管理交到德才兼备者手中。孙氏也主张,那种通过适宜的教育而具备了行政管理能力的人应该被挑选出来担任政府的各种职位,并且除了品格和能力之外不论其他条件。 [491] 科举制度就是力图将这些原则付诸实施。
**孙中山并不想全盘照搬帝制下的科举制度。他(像孔子一样)是非常敏感的,不认为仅仅是拥有古代书本的知识就能使一个人胜任官职。但他确信欧洲和美国的民主政治相当缺乏他所希望的东西,并且他还对虚伪的人类平等的概念大加谴责。他更甚于孔子或杰弗逊,不相信那种世袭贵族制。但他却同孔子和杰弗逊一样,认为事实上“人并不是生来平等的”。 [492] 唯一能够实现的一种平等就是机会平等。他说:“如果我们对于个人之间才智和能力的不同视而不见,而把那些杰出的人物拉下来,以便坚持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那么,人的品性就不会进步而只会退步。因此,当我们讲求民主和平等的时候,尽管希望世界进步,但我们只是讲政治的平等。因为平等并不是自然给予的东西,而是人创造的东西,并且人所能造就的唯一的平等就是政治地位的平等。” [493]
所以,孙中山认为,尽管每个人都应该有管理政府的平等权力,但是,通过选举,只有那些拥有必备知识和才能的人才会取得官职。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能够使自己拥有这种资格的平等机会,但他们的资格应该接受科举考试的检验。所以,他做出计划,要求“所有的从政候选人,无论是选举的还是任命的,国家的或地方的,都必须首先通过中央政府主管的考试,以便确认他们拥有了必要的资格”。 [494]
在这种体制中,出现政治操纵的可能性是明显的。可是,孙中山希望把政府各个单独的机构自行组织的考试统一归属于考试院,以使这种可能性缩小到最低程度。考试院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帝制下的翰林院。
有了西方人所采用的三个权力机构,再加上两个源自儒学的机构,孙中山相信将有可能矫正西方民主政治的缺陷,并建立起“世界上最圆满的和最良好的政府”。 [495]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愿望无论有何长处,都不曾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的中国政府实际运作的基础。因为它尽管包括有监察院和考试院,但在当今这样的社会转变时期,这些机构从未得到过孙中山所希望它们得到的用武之地和权力。
未来的中国人将如何评价孔子,恐怕只有未来才能告诉我们。然而,无论他们是赞颂孔子的名字还是忘掉它,在此后的很长时期内,所有中国人无疑还会继续受到孔子的影响。莱茵伯格在1938年写道,儒学仍旧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独一无二的文化力量”。 [496] 林语堂在1943年断言:“儒学作为中国人民之中的有生命力的力量,仍在继续塑造着我们民族的处世行为……” [497]
这样的思想至少有一些程度的真理性,并可能在1945年得到了证明。那时,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的话语让那个号召筹组联合国的会议感到震惊,他宣布说,中国“在与其他国家进行联合的问题上,已经准备好了必要时放弃一部分主权给予这个新的国际组织”。 [498] 其实,在发生此事的21年前,孙中山就指出:“欧洲近来提议的世界主义,中国于2000多年前就在讨论了。”作为这一事实的证明,他提到了一部儒家经典。 [499]
注释
[1] ——译按:也就是说,对于孔子创立的思想学派,人们习惯上称作“儒家”,而不是“孔家”,近代以来“孔家店”的称呼是明显的蔑称。从Confucius(孔子),到Confucians(儒生)和Confucianism(孔学),这种西文用法上的孔子与儒学在造字用词上的联系,是西方传教士们的发明,不是中国古代的习用。当代中国有“孔学”之类的用语,但孔学并不等同于儒学。
[2] 《论语·阳货十七》:“吾其为东周乎?”
[3]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4]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公孙丑下》、《孟子·离娄上》;《荀子》(2),第112页。
——译按:《荀子·富国》:“故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使而功,撞钟击鼓而和。”
[5] 胡,第151页。
[6] 《孟子·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章。
[7] 《韩非子·显学》:“自孔子之死也……儒分为八……皆自谓真孔。”
[8] 《史记·儒林列传》:“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弟子传》:“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
[9] 《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去齐宿于昼”章、《离娄下》“曾子居武城”章、《万章下》“万章问曰敢问友”章及“万章曰士不托诸侯”章、《告子下》“淳于髡曰先名实者”章。
[10] 《孟子·公孙丑下》、《孟子·离娄下》、《孟子·告子下》、《孟子·万章下》,同上注;《孟子·尽心下》:“说大人,则藐之。”
[11] 《荀子》(2),第109、135页。
——译按:《荀子·不苟》:“君子……参于天地。”又《非十二子》:“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
[12] 《孟子·公孙丑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万章上》:“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
[13] 《孟子·尽心上》:“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14] 《孟子·梁惠王下》。
[15] 《孟子·公孙丑下》:“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尽心下》:“孟子之滕,馆于上宫。”
[16] 《盐铁论》(2),第66页。
——译按:《盐铁论·论儒》:“御史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
[17]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18] 《韩非子·五蠹》。
[19] ——译按:《韩非子·五蠹》:“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
[20] 《庄子》卷一,第288页。
[21] ——译按:《孟子·告子上》:“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
[22] 《荀子·儒效》:“逢衣浅带,……术缪学杂,……其衣冠行伪(为)已同于世俗矣。……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
[23] 《礼记·儒行》。这句话被认为是孔子所说,而《礼记》的整个这一章明显是后来写成的和不足凭信的。见本书注 。
——译按:《儒行》:“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
[24] 见本书注 。
[25] 《墨子·非儒下》:“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夫(春)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餍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26] 《论语·八佾第三》“林放问礼之本”章;参见《子张十九》:“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27] 柏拉图(4),第695页。
[28] 《孟子·尽心上》:“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亦见于《国语》卷五和《书》第466—468页。后一种资料中的观点与上文引述的柏拉图的那一段很相似。它来自《无逸》,这一篇不是(如它自称的那样)远到周公时代的作品,但它可能是汉代以前的作品。
[29] 《论语·为政第二》“君子不器”章、《子罕第九》“大宰问于子贡”章和《子路十三》“樊迟请学稼”章。
[30] 当然,我们没有忘记,《礼记》的很大部分是《荀子》的模本。但在此我讲的是“更粗俗乏味的那些部分”。
[31] 《墨子》(2),第82、189、239页。
——译按:《墨子·非命中》:“自古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兼爱中》:“诸侯相爱则不野战。”
[32] 胡适对这本书的批评(胡,第151—152页)我认为是很精彩的;亦见冯,第80—81页。
[33] 《淮南子·要略》。
[34] 《墨子》(2),第237—238页。
[35] 《墨子》(2),第125页。
——译按:《节葬下》:“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诸侯死者,虚车府。”
[36] 《论语·八佾第三》“林放问礼”章、《子罕第九》“子疾病”章和《先进十一》“颜渊死”章。墨子说,在他那时,有许多“士”和“君子”怀疑厚葬和长期守丧是否妥当[《墨子》(2),第125页]。墨子也攻击了三年守丧的做法,而正如我们所见,孔子对此有明确的倡导。
[37] 《荀子·礼论》。
[38] 《墨子》(2),第219、230—233页。
——译按:《墨子·公孟》:“君子共(恭)己,待问焉则言,不问焉则止。譬若钟然,扣则鸣,不扣则不鸣。”
[39] 《墨子》(2),第201页注[1]。亦见胡,第151页。许多事情不自觉地暴露出了《非儒》篇的作伪特点。在其中,并且明显地只是在这一篇中,孔子被称作“孔某”。用这种方式讲说孔子是在儒家学派中流行起来的,因为极端的孝行禁止称呼夫子个人的名字。可是,这种用法是后来才有的;它并未出现在《论语》,也没有出现在《孟子》之中,尽管孟子晚于墨子并且是一位良好的儒者。在这一篇中,对孔子的攻击是最不合情理的。
——译按:关于顾氏对“孔某”这一称呼的误解,见本书注 中译者的辩正。
[40] 《墨子·公孟》。
[41] 《墨子·贵义》:“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攈禾也。”
[42] 冯,第84页。
[43] 《墨子·尚同中》:“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则诛罚之。”
[44] 引自芬纳,第19页。
[45] 《墨子·尚同中》:“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又见《非攻》等篇。
——译按:《非攻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
[46] 《墨子·节葬》、《墨子·明鬼》、《墨子·公孟》等。
[47] 《墨子·贵义》:“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
[48] 卡伦,第310页。
[49] 《论语·泰伯第八》“禹吾无间然”章和《宪问十四》“南宫适问于孔子”章。
[50] 正如我们指出的,这一原则不断地在《论语》中出现,特别是《为政第二》“哀公问”章和《颜渊十二》“樊迟问仁”章。顾颉刚说后一章是后来插入《论语》的,并且“显示出墨家的影响”,见顾(6),第55页。但是,既然孔子在墨子之前,这个表述便只能说明,如果它是真实的,孔子就没有倡导过人应该依据他们的才能被提拔,而事实上,这种观念在《论语》中是很普遍的。上述《颜渊十二》中的观点之所以被怀疑,因为说是“它在这一篇的末尾处”,这是不太严密的说法。这一章后面还有两章,看上去也没有什么问题。而这一章,不仅不是晚出的,而且还是很早的。如果它和《孟子》或《论语·尧曰二十》首章一样地晚出,那么,舜就可能是要提拔禹,而不是皋陶了。
——译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顾颉刚等人为首的“古史辨”运动中,认定关于尧、舜、禹的传说全部出自墨家的杜撰。这种观点在当时很轰动,但后来却逐渐被学术界所放弃。总的说来,顾氏所使用的“辨伪”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考据材料方面却失之粗糙,且有强烈的先入之见。比如对《论语》中有关这些上古之王的记载,如果先认定它们是墨家插入的,然后再以此证明此类传说是墨家的发明,这便是使用了不合理的循环论证的方法。
[51] 见顾(6)。在我看来,这项研究做出了错误的假定,即认为儒学实际上具有更纯粹的特质,也就是说,儒学一贯根据的是这样的原则:“对亲戚特别钟爱,尊敬那些达之于高位的人(亲亲贵贵,第31页)。”但这是非常令人怀疑的,特别是当我们探究它在孔子本人那里的情形时,尤其怀疑那种说“贵贵”可以合适地称作是儒学基本原理的说法。而且,墨子激烈地批评儒生,而孟子则进行了回击。如果古代选择帝王是以德行为基准的思想是墨家首创的话,那么,只有这样的事实才是可能的:墨家人物应该反对儒生对这种观点的偏爱。然而,墨家人物却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其例可见《孟子·万章上》“墨者夷之”章。正如冯友兰所指出的,《墨子》之中《墨经》部分(一般认为代表的是后期墨派的思想)批评以尧和舜为楷模的做法清楚地说明了墨家“对儒家尊重圣人的攻击”(冯,第274—275页)。这并不支持这样的看法,即关于尧和舜的传说是墨家的发明。
[52] 《墨子·公孟》:“公孟子谓墨子曰:‘昔者圣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
[53] 《孟子·万章上》。
[54] 如果孔子相信,甚至还创立了这种思想,就应该在《论语》中提及,但是,《论语》并没有提到过这种思想(除了《尧曰二十》首章,这一章是后来加进文本中去的)。而且,从《颜渊十二》“樊迟问仁”章来看,子夏也不知道这一学说。如果子夏知道这种观点,那么,为了更能说明问题,子夏应该举出选择天子的例证,而不会只提到挑选大臣的事情。《孟子·万章上》有一节引用了孔子的话,说的是尧和舜的禅让故事,但顾颉刚说此处使用的语言是不合乎时代的。他还认为,《论语》的这一章是后来插入的,见顾(6),第56页。无论如何,认为孔子做出过这种陈述的说法是令人怀疑的。
[55] 详见《史记·燕世家》。
[56] 《战国策·燕策》。《韩非子》有许多种这个故事的不同形式,在最后的一个故事里,说这是燕王甘心情愿的禅让(《外储说右下》)。
[57] 事实上,他到此为止至少是默许了齐国对燕国的进攻,而自进攻之后燕国就陷入了混乱;见《孟子·公孙丑下》。《战国策·燕策》说孟子明确地煽动了这次进攻。
[58] 《孟子·万章上》。
[59] 《荀子·正论》。
[60] 《汉书》(2),卷一,第218页。
[61] 详见《汉书·文帝纪》和《史记·孝文本纪》。
——译按:《史记·孝文本纪》:“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实,专制帝王如此举动,原非出自本意,而是考验臣下的忠心。
[62] 确实,《孟子·万章上》中的几节提到了影响这种情况发生的种种传统说法,但不能确定的是,它们详尽阐述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
[63] 我的这个结论是以对文献和金文的考证为基础的。顾颉刚持相同的观点,并引证了多方面的丰富证据,见顾(6),第33—42页。
《孟子·告子下》有一段文字,讲的是齐桓公会盟诸侯时所制定的誓约中的一项条文:“士人不得世袭做官(士无世官)。”这段文字是很奇特的。从后文特别提及的“大夫”来看,这个要求看上去只是专门针对低级官员提出的。孟子这么表述,很可能是为了他所倡导的世袭占有高官(世卿世禄)的观点作铺陈的(《梁惠王下》、《滕文公上》)。顾颉刚指出,在《公羊传》和《穀梁传》中,这个誓约中的词语是相当不同的,并认为孟子的表述是不可靠的[顾(6)4.1]。确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孟子的表述看上去是很奇怪。
[64] 公正地讲,孔子显然不知道这种书的内容,然而,孟子却点出了它的书名并引用了它的内容(《孟子·万章上》)。顾颉刚认为,现存《尧典》仅仅是完成于汉代,顾(6),第98—99页。
[65] 顾立雅,第55—89页。
[66] 《孟子·尽心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译按:根据《孟子》的上下文,孟子所说的“不如无书”,并不是说这种书是伪书,而是说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这种书籍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因为记述者对事件总有一些夸张性或渲染性的描写。另外一个非常值得强调的事实是,这个时代的所谓伪书,只是想通过古人表达今人的思想,并且重在表达愿望,而不是作者个人从中获利,因为写作这种伪书者并没有留下个人的痕迹。
[67]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受业子思门人。”
[68] 崔,卷四。
[69] 《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致为臣而归。”《告子下》:“夫子在三卿之中。”
[70] 《孟子·万章上》“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章、“万章问曰人有言”章;《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71] 《孟子·梁惠王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
——译按:照一般的理解,孟子所谓“国人”,指的是贵族阶层,不包括普通百姓。“国人”的另一种常见的解释是都城之中的所谓自由民。
[72]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章;《公孙丑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
[73] 《孟子·梁惠王上》末章、《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章、《公孙丑上》“孟子曰尊贤使能”章和《滕文公下》“彭更问”章。
[74] 《孟子·梁惠王上》首章,《滕文公下》“彭更问”章,以及《论语·里仁第四》“放于利”章、“君子喻于义”章,《子路十三》“子夏为莒父宰”章,《宪问十四》“子路问成人”章和康德(2),第66页。
[75] 《论语·子路十三》“苟正其身”章。
[76]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谓齐宣王”章、“齐宣王问曰汤放桀”章,《公孙丑下》“沈同以其私问”章和《万章下》末章。
[77] 《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谓媸娃”章。
[78] 《孟子·万章下》“万章问士之不托诸侯”章。
[79] 《孟子·万章下》“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和《尽心上》“孟子曰古之贤王”章。
[80] 《孟子·离娄下》“曾子居武城”章。
[81] 《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去齐”章,参见《尽心上》“孟子自范之齐”章。
[82] 《孟子·万章下》“君子有三乐”章。
[83] 《孟子·离娄上》:“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84] 《孟子·梁惠王下》:“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欤)?”
[85] 《孟子·梁惠王下》“为巨室”章、《公孙丑上》“以力假仁者”章和“仁则荣”章。
[86] 《孟子·滕文公》首章、《离娄下》“储子曰”章和《告子下》“曹交问曰”章。
[87] 《孟子·梁惠王下》首章,《公孙丑上》“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章、“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离娄下》“大人者”章、“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章和《尽心下》“尧舜性者也”章。
[88] 《孟子·尽心上》:“万物皆备于我。”
[89] 《孟子·尽心上》。
[90] 洛兰·克里尔,第72—74页。意味深长的是,尽管《孟子》的字数是《论语》的两倍,但“学”字的出现,《论语》却是《孟子》的两倍。
[91] 《论语·为政第二》:“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92] 《孟子·离娄上》:“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93] 《孟子·离娄上》:“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94] 《孟子·离娄上》:“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
[95] 《孟子·告子下》“白圭”章。
[96] 冯,第108页。
[97] 比如,在《孟子》中我们没有看到孔子讲说数字,即“三”、“九”之类的说法,而在《论语》的后来部分中,孔子的话语中却大量地使用了数字。关于《论语》的这些后来部分的具体情况,见本书“附录”的讨论。
[98] 《孟子·公孙丑上》;《万章上》“万章问人有言”章和《万章下》首章。
[99] 《孟子·万章上》“咸丘蒙问”章和“万章问曰或谓孔子”章。
[100] 《孟子·滕文公下》“周霄问”章,《告子下》:“孔子为鲁司寇。”
[101] 尽管《墨子·非儒》说孔子是鲁国司寇,但是,《非儒》篇中的这种记述,至少是这一篇中的这部分,可能是晚于《孟子》的。见本书注 。
[102] 《孟子·万章下》“北宫锜问”章。
[103] 《孟子·尽心上》:“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104] 《孟子·尽心上》:“王者之民,皋皋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
[105] 例如,比较《老子》80章等。事实上,这并非不可能是道家的东西插入到了《孟子》之中。有必要指出的是,以上所引三章均在《尽心上》,而其他地方都不是以这种方式和提及“天地”的。
[106] 见韦利(3),第49—50页。
[107] 有关这种争论的结果可谓卷帙浩繁。崔述反对《老子》成书年代很早的观点;见崔,卷一。在有鉴赏力的学者之中,胡适为传统的观点作辩护,认为此书成书很早;见胡(5),第103—104页。韦利大胆地提出了最确定的日期,他说,这本书是被“一位匿名的无为主义者”“在大约西元前240年”写成的(韦利[3],第86页)。
洛兰·克里尔(第27—35页)指出,《老子》攻击了某种孔子之前尚未出现的学说,而且它反复使用的一些言辞并未出现在早于《墨子》和《孟子》的文献中。
[108] 《庄子》,卷一,第197页。
——译按:《庄子·齐物论》:“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
[109] 《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欤),蝴蝶之梦为周与(欤)?”
[110] 《老子》,第18章、38章。
[111] 《老子》,第19章、48章、80章;《庄子》,卷一,第198、255—256、288—290页。
[112] 《老子》,第81章:“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113] 《老子》,第19章:“绝学无忧。”
[114] 《庄子》,卷二,第177页。
——译按:《庄子·盗跖》:“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
[115] 《老子》,第30章、31章、57章、69章、74章、75章。
[116] 《老子》,第44章。《庄子》,卷一,第167—170、390页;卷二,第149—165页。
[117] 《庄子》,卷二,第153—154页。
——译按:《庄子·让王》:“道之真以治身。”
[118] 《庄子》,卷一,第261页。
——译按:《庄子·应帝王》:“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119] 《老子》,第56章。
[120] 《老子》,第5章;《庄子》,卷一,第332—333页。
[121] 《老子》,第3章:“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122] 《庄子》,卷一,第305页。
——译按:《庄子·在宥》:“粗而不可不陈者,法也。”
[123] ——译按:1993年冬,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的一号楚墓中出土了举世瞩目的“郭店楚简”。这座墓葬属于战国中期偏晚的时代,从中发掘整理的简片有多种古籍,包括迄今为止人们所见到的最早的《老子》传抄本。在这本《老子》中,并没有刻意对孔子或儒家思想的批评或攻击,这是个意味深长的事实。它说明,或者最早的《老子》版本早于孔子时代,或者撰写这个版本之《老子》的人不了解孔子或儒家思想。但是,一个可能存在的事实是,《老子》和道家思想对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攻击开始于战国中晚期,而后来的《老子》是经过了重大修改和增补的。
[124] 《庄子》,卷一,第228—229、255页;卷二,第135—136、166—167、180页。
[125] 在一些这样的故事中还提到了颜回,但《论语》数次记载了颜回之死。
[126] ——译按:《论语》所记孔子言论中,确实有一些消极避世的内容,但这是他晚年周游列国屡屡受挫时的情绪发泄,而不能被视为道家思想的表述,因为孔子的此类言辞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思想观念。
[127] 《庄子》卷一第211页孔子讲出了“阴阳”这个词;而这个词的晚出的日期可见本书注 。
[128] 《庄子》,卷一,第354—362页;卷二,第144页。
[129] 《庄子》,卷二,第192—201页。
[130] 《庄子》,卷一,第166—176页。这一篇(《盗跖》)提到了子路之死,但此事发生在孔子71岁之前。
——译按:《庄子》一书本有寓言成分,重在阐述思想,并不在意史实,书中所言孔子及孔门弟子的故事,基本上不能作为研究孔子生平及思想的依据。庄子之书之所以选择孔子为其故事的主人公,多半是想借孔子之名传播庄学,不一定是纯粹诋毁孔子。当然,从庄学借用孔子之名的事实中也可看出,到了战国中晚期,孔子及儒学已经在当时社会形成了巨大影响。
[131] 长久以来,人们就认识到《论语》中某些有关隐居者的章节显示出了道家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我怀疑《季氏十六》“见善如不及”章和“齐景公”章、《微子十八》“楚狂接舆”章和“逸民”章。比较《庄子》,卷一,第319页;卷二,第120—121、135—136、153、192—201页。
《阳货十七》“予欲无言”章可能是道家插入的。对于子贡传递孔子学说的自我意识的提及看上去也是后来附加上的。情感是孔子的,而语言却像是道家的。“百物”的用法不符合孔子的思想;事实上,“物”字未出现在《论语》的其他地方。比较《老子》第1章和第43章,以及《庄子》,卷一,第335—336、338页;卷二,第3—5、104—105、121、128页。
——译按:古代隐士的出现远早于孔子时代,而在孔子所处的动乱之秋,隐士的存在自不必说。孔子在外周游十几年,不可能不与这些人士相遇。特别是在周游后期,孔子政治上的彻底失意很可能会导致思想的偶然波动,以至于与隐士进行思想交流,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老子思想不管有多早,也不会是无源之水;而与孔子相遇的道家人物,并不一定与老子有直接关联。在那种百家争鸣的时代,如果《论语》中没有丝毫的道家思想或者与道家思想相似的思想痕迹,那才会让人感到奇怪呢!也就是说,也有一种可能是,《论语》中的孔子思想影响了道家思想的产生,如果《老子》的出现在《论语》之后的话。
[132] 《老子》,第47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133] 有必要对汉字“阴”和“阳”的使用作如下区分:一种情况是,它们中的某一个偶尔被使用;另一种情况是,它们作为哲学概念而出现。在《易经》原初部分、《尚书》今文经、《诗》和《论语》中,均未出现此概念,甚至晚至像《孟子》这样的儒家著作也没有出现过。这两个字也没有出现在甲骨文中。孙海波在他的《甲骨文编》(14.5a)中识别出了“阳”字,但显然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判断错误,因为那并不是一个可以确切辨认的刻字,见严,5.47a。董作宾向我保证说,在他20多年的甲骨文研究中,从未遇到过这两个字(1947年10月21日的口头会谈)。在前儒家时期的金文中也未见到此概念。它们出现在除最后两篇以外的所有《易经》“十翼”中,即《易经》,第223、224、267、355、357、359、388、395、414、420—424、426页。
[134] 这可能是在《论语》可疑的最后5篇中频繁出现数字的原因。尽管《孟子》中的孔子没有此类说法,但是《庄子》(卷二,第209页)所引述的孔子之语却列举了他对小人的“九试”。(《庄子·列御寇》)
[135] 顾(3);韦利(3),第141页。
[136] 这个结论差不多是由《易经》第392页对颜回的提及而做出的。
[137] “地”字在早期文献中是罕见的,在讲到“大地”时,通常用“土”字来表示。孙海波在《甲骨文编》中未列此字,而董作宾也向我保证说,他在商代甲骨文中从来没有见到过此字(1947年10月21日的口头谈话)。容庚在他的《金文编》对金文的分析中也未提到此字,而郭沫若亦在1932年写道,在早期金文中“没有看到”作为天之对应部分的“地”字(郭,31b)。在《易经》中,这个字只出现过1次(《易经》,第135页。——译按:《明夷》:“初登于天,后入于地。”),但却并不是形上意义的。在今文《尚书》中,它出现了3次(《书》,第245、354、593页)。所有出现此字的那几篇文献均被认为是在相对晚期写成或编成的,然而,即使这样,“地”字也没有形上意义。在《诗》中它出现了3次(《诗》,第307、317页),但都是形下之大地的意思。《论语》中它出现了3次(《子罕第九》、《宪问十四》和《子张十九》),也没有形上意义。《孟子》中此字很常见,但仍不能确认它是个形上概念(《告子上》“霸者之民”章“上下与天地同流”,其中的这个“地”字是有争议的)。
在“十翼”中,“地”字出现了许多次,尽管在最后两篇中没有发现。但是,在其他各篇中,它是作为明确的形上概念出现的,比如《易经》,第226、227、233页等。
[138] 《易经》,第354、366页。
[139] 见下文,英文原著第201页。
[140] 《书》,第367页。
[141] 《左传》中的例子很多,如《定公十四年》、《哀公七年》等。
[142] 《易经》,第351、369页。
——译按:英文原书称《易经》,应该指的是《易传》,即前文译称“《易经》的附加部分”。严格说来,《周易》由两部分组成,即《易经》和《易传》,英文原著有时对此区别不明。
[143] 对这一结论的表述包括以下著作:冯,第381页;冯(2),第198—201页;傅(中),第61—62页;本田,第50—53页;德效骞。
——译按:孔子与“十翼”的关系学术界已有定说,恐怕没有人还会认为孔子是这些篇章的作者。不过,仍有一些道家思想的研究者为“十翼”的归属煞费苦心,认为它们是道家的著作。正如本书下文所言,“十翼”是儒、道两家思想的混合物。然而,从总体上说,它们是战国末期儒家者流所著,尽管这些作者深受当时道家思想的影响。
[144] 《论语·子路十三》:“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参见《礼记》,卷二,第363页。我把这一章译为:“夫子说:‘南方人有种说法:一个没有恒心的人甚至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巫士或医生。(说得)好啊!如果他的德行反复无常,就容易招致耻辱。仅仅去问卜是不够的。’”孔子的引语——“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出自《周易》(“恒”卦“九三”爻辞),但孔子之所以知道它,仅仅因为它是一条格言。以上译文部分地与韦利的翻译相同。
——译按:《礼记·缁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欤)?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侦,妇人吉,夫子凶。’”
[145] 傅(中),61b。
[146] 《荀子》(2),第104页。
[147] 吉本,第389页。
[148] “十翼”的一些章节极相似于道家著作,比较《易经》第213页和《庄子》卷一,第171页;《易经》第226页和《老子》第24章、第34章、第36章等。
[149] 《易经》,第359页。
[150] 《易经》,第389页。
[151] 《庄子》,卷一,第57—58页。
——译按:《易传·系辞下》:“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庄子·知北游》:“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
[152] 《论语·卫灵公十五》:“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153] 《庄子》,卷一,第355、360页。
[154] 《经典释文》说:“鲁读易为亦。”许多学者认为这就意味着《鲁论语》在此处是个不同的字,但江心诚认为这种解释只关乎发音;见《伪书》,第71—72页。德效骞认为,整个这一章都是后来插入的;见德效骞。
——译按:释“易”为“亦”,属下句,则“五十以学”就无法理解了。实际上,《易》的最初用途是占卜之书,但卦辞和爻辞的内容却是先民的生活经验之总结。正是在此意义上,孔子才去学习《易经》。不能因为《易经》是占卜之书,也不能因为《易传》的思想相对肤浅,就否定孔子与《易经》的任何联系。《论语》此章应该理解为,晚年孔子检讨自己在从政方面的失误时假设说,如果再倒退若干年,让我在50岁从政之前就读《易》,我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失误了。这显然是说,《易》中的思想有助于孔子在政治上表现得更为成熟练达,特别是在与鲁国“三家”的政治较量中。
[155] 它只出现在现已亡佚的《庄子》的残篇中,但《太平御览》849.2a引用了它。在这个文字有所错讹的章节中,子路想给孔子问卜,孔子回答说:“我的占卜已经做过了(——译按:“丘之祷久矣。”)。”对此书的参考,我受惠于韦利,第131页注[3]。
[156] 《论语·子罕第九》:“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157] 顾(5),第9页。《论语》还有一次提到了凤凰,那是出自《微子十八》中的一位道家隐士之口。这一章无疑也是在早已指出过的道家影响下而后加的。事实上,在《庄子》卷一,第221页有一件与此相关的同样的事情,其语言也有某种程度的相同。河图在“十翼”中被提到,见《易经》,第374页。在《尚书》的一篇早期文献中,也提到了河图(《书》,第554页),这一事实对于我们现在的讨论并无重要意义。对河图没有什么可说的,那可能仅仅是一幅地图。
[158] 根据不同学者的看法,这个日期可能有上下一个世纪或者更多时间的偏差。马伯乐的有关预言日期的研究使得《左传》成书的日期很难早于西元前300年,但是,可能总有一些后来插入的章节。见马伯乐(2)和卡尔格伦。
[159] 常镜海,第5页。
[160] 这些预言的经常性是令人惊讶的。我作过统计,在西元前541—前537年的5年间就有25次之多,而在其他时期可能还会更多。我没有核实所有这些预言的精确性。
[161] 马伯乐(2),第191页。
[162] 详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左传·襄公三十年》、《左传·昭公七年》、《左传·昭公八年》、《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等。
[163] “五行”的发生日期并不完全清楚。韦利写道:“一般来讲,我见到的大部分中国和日本学者都没有理由认为五行理论早于西元前4世纪。”韦利(3),第109页注[1]。“五行”至少有一次出现在《墨子·经》中,但是,这部分一般被认为是相对晚些时候的篇章。有人认为“五行”理论存在于孟子时代(见陈梦家)。陈梦家在第46页引用的证据显示,带有这种思想的理论发端于孟子时代,但并不必然证明“五行”概念存在于此时。他引自《荀子》的证据并不具有结论性,因为有证据表明,《非十二子》篇中的这一特殊部分是后来插入的。见《荀子》(3),3.12b。《孟子》从未提及“五行”这一事实使这一切更为可能了。
[164] 《左传·文公十八年》。
[165] 《左传·宣公十一年》。他后来在带走了许多人质之后,又撤出了这个国家,可能是由于害怕其他国家的报复。
[166] 《左传·成公二年》。
[167] 《左传·宣公十一年》、《左传·宣公十二年》。
[168] 麦考利,第352—353页。
[169] 《左传·昭公十七年》、《左传·哀公六年》、《左传·哀公十四年》。
[170] 《左传·昭公七年》。既然孔子能为他兄长的女儿择婚(《论语·公冶长第五》),他显然是家族的首领。
[171] 《左传·宣公二年》、《左传·成公二年》。把其中的第一段话归之于孔子的做法受到了《钦定春秋》(卷二十)的批评。对其第二段,理雅格指出,“批评家一致认为,这一段不能归之于孔子”。
[172] ——译按:顾氏在本书中对于《左传》特别是《左传》有关孔子记载的评价,深受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界所谓疑古之风的影响。在本书中,他一方面肯定了《左传》在记载史实方面是可信的,另一方面又怀疑该书中有关孔子记载的历史可靠性。他一方面认为《左传》不应该加入太多孔子的记载,以此来证明《左传》乃儒生出于政治目的而编纂;另一方面又指出《左传》没有孔子传记或缺乏足够的孔子传记的材料,以此来证明《左传》有关孔子的史实是值得怀疑的。总之,在顾氏看来,不管是《左传》还是其他书籍,关于孔子的记载,如果太多了,就被认为是编造;如果太少了,又会说凡是没有提及孔子生平事迹的,就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充分说明,顾氏对于《左传》及《左传》记载孔子史实的置疑是结论在先、论证在后的。
[173] 《钦定春秋》,卷三十五。
[174] 高本汉,第58—64页。
[175] 《国语·鲁语》。
[176] 为较早日期所作的辩护,见韦利(3),第137页和哈伦,第456—460页。像许多别的学者一样,伯希和认为现存《孔子家语》乃王肃伪造,此人卒于西元256年,见伯希和,第421页注[430]。
[177] 《孔子家语》,卷二、卷三、卷十。
——译按:《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吾以为夫子无所不知。”
[178] 《孔子家语》,卷七。
[179] 《孔子家语》,卷七。
[180] 《孔子家语》,卷四、卷七;参见《论语·颜渊十二》“季康子问政”章和《子路十三》“樊迟问仁”章。
[181] 《孔子家语》,卷一、卷二。
[182] 比较《老子》第47章首句和《孔子家语》卷二中的句子。崔述指出,这部书也大量借用了《庄子》和《列子》的内容;见崔,卷三。《孔子家语》把大量书籍中有关孔子的内容杂凑在一起。在上述剽窃《老子》后的第4页又抄袭了《孟子·梁惠王下》的一大段,并把它引述为是孔子所说。
[183] 《孔子家语》,卷三。
[184] 《史记》,卷五,第299页注[4]。
[185] 戴闻达(2),第95页;钱穆,第101页。
[186] 戴闻达,第221页。
[187] 《荀子》(2),第175—181、275页。
[188] 这一点我曾得益于洛兰·克里尔,第136—137页。
[189] 《荀子·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190] 《荀子·性恶》。
[191] 《荀子·荣辱》:“故先王案(乃)为之制礼以分之。”
[192] 《荀子·修身》:“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
[193] 《论语·述而第七》“盖有不知而作”章。孔子和他的直传弟子们提出了对“学”这个词的宽泛解释,事实上,他们也并未优先强调单纯的书本学习,见《学而第一》“子夏曰贤贤易色”章和“君子食无求饱”章,以及《雍也第六》“季康子问”章和《子路十三》“诵诗三百”章。
[194] 《荀子》(2),第184、264页。他对道家形而上学的反对,《荀子》(2),第96页。
[195] 《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196] 《荀子·修身》:“不识步道者,将以穷无穷、逐无极与(欤)。”
[197] 《荀子·修身》、《荀子·荣辱》、《荀子·儒效》、《荀子·解蔽》等。
[198] 《荀子·劝学》:“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199] 德效骞,第108页。
[200] 《荀子·正名》:“故明君临之以势,道(导)之以道,……禁之以刑。”
[201] 冯,第311页。
[202] 《荀子·王制》。
[203] 《论语·子路十三》“子适卫”章;《荀子·富国》。
[204] 《荀子·富国》。
[205] 《荀子·儒效》。
[206] 梁,第151页。
[207] ——译按:这应该是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的李斯对韩非子的迫害。
[208] 对于《韩非子》,我主要依从陈启天和容肇祖的校勘本(见“参考书目”)。
[209] 《韩非子》,16.7a,18.6a;《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译按: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老子和韩非子合在同一篇传记中,并非偶然。至少在司马迁甚至西汉时代的某些学者看来,韩非子和老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所以,盛行于西汉早期的黄老之学,在“休养生息”的背后,潜隐着对社会进行专制统治的玄机。
[210] 包德,第112—119页。
[211] 《商君书》,第291—292页。这部书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商鞅本人所著,而且这一段可能也不是它的最古老的部分,但其内容却是相当法家式的。参见《韩非子》,2.10a;书中的这部分不可能是韩非子所写,但却清楚地表现了法家思想。
——译按:《商君书·画策》:“是以人主处匡床之上,听丝竹之声,而天下治。”
[212] 《韩非子》,19.1、3.17。
[213] 齐思和,第182—187页。
[214] 《韩非子·五蠹》:“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而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
[215] 《商君书》,第181、186、303页;《韩非子》卷十八、十九。参见《老子》第3、19、65章。
[216] 《老子》,第65章:“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217] 齐思和,第166页。
[218] 《商君书》,第125页;参见第24页。亦见《史记》卷二,第44—45、62页;卷五,第179页。《荀子》(2),第311—312页。包德,第2—3、7、19—20页。
[219] ——译按:《荀子·强国》:“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汙(污),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
[220] 《商君书》,第1—40页。齐思和还提到,商鞅改革的突出部分包括把众所周知的魏国的做法(李悝之法)移用到秦国,而商鞅曾在魏国做官;见齐(2)。
[221] 《史记·李斯列传》;包德,第14—15、50页。
[222] 《荀子·王霸》。
[223] 《韩非子》卷十七、十八、十九。
[224]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钱穆(第442—443页)对此有疑问。我同意包德的看法,此事是很有可能的。可是,我同意钱穆的另一个看法,即秦国迫使韩国派韩非子前往秦国的故事是荒唐的。
[225] 《史记·秦始皇本纪》。
[226] 《史记·秦始皇本纪》。
[227] 那就是说,所有的道路都有相同距离的车辙。这样一来,各种车辆,特别是帝国的战车,就能轻易地四处奔驰。
[228] ——译按:《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229] ——译按:《史记·秦始皇本纪》:“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230] 《史记·秦始皇本纪》。
[231] 《史记·秦始皇本纪》。
[232] 亚里士多德,第1312—1313页。
[233] 《韩非子》卷十八、十九。
——译按:《韩非子·五蠹》:“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
[234] 《史记·秦始皇本纪》。
[235] 《史记·秦始皇本纪》。
[236] 《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活埋(殉葬、人祭)”,见包德,第117页注[3]。
[237] 《史记·秦始皇本纪》。
[238] 包德,第163—165页。
[239] 《韩非子》卷三、十一、十四。
[240] 《韩非子》卷九、十一。
[241]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中有一个故事的两种说法。这个故事说,在殷代,往街上倒灰的任何人都要受到严重的惩罚,一种说法说要砍断倒灰者的手。孔子对此很赞成,并说:“让人民去做容易的(不倒灰)以避免出现他们不喜欢的(惩罚),这是治国的合适方法。”这种陈述集中体现了法家思想。在讲了这个故事之后的第二页,这种说法又被归之于法家商鞅(只有个别字作了微小的变动)。根据李斯的说法,对倒灰于街上的人进行惩罚,这是商鞅为秦国建立的法律条文(《史记·李斯列传》)。整个思想与孔子在《论语·子路十三》所说的“赦小过”截然相反。
这些轶事都由W. K. 廖进行了翻译,但在两处地方,结论和关键句子都理解有误[《韩非子》(2),第293—294页]。
[242]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243] 度量衡的统一见《书》第36页。整个“吕刑”篇都是真正的法家式的。
[244] 《荀子·宥坐》等篇;崔,卷二;钱穆,第22—23页。
[245] 崔(2),卷三;冯,第369—371页;休中诚,第86—87页。
[246] 《礼记·中庸》:“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一段下面的文字是:“尽管一个人可以登上王位,如果他没有必需的德行,就不可以冒险建立(原意是制作)礼和乐。如果一个人具有德行,如果他没有王位,也不可以冒险去创建礼和乐。”(“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这里,在前一句中,占据优先地位的法家思想被儒家的修改给软化了,而第二句则又返回到了法家思想。
[247] 《史记·秦始皇本纪》。
[248] 《韩非子》卷十九;《史记·秦始皇本纪》。
[249] 《家语》卷一。
——译按:《孔子家语·五仪解》:“生今之世,志古之道。”
[250]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稀)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稀)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稀)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译按:顾氏以为此章颇受法家影响,其实这是苛求。孔子强调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地位,是以周朝的分封制为基础的,这与法家式的中央集权有本质上的不同。
[251] ——译按:孔子所谓的“庶人不议”,是说国家走上轨道之后,普通人的生活有了保障,自然不必议论国政,并不是说不允许议论。至于“教民”,与此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在周朝初期就有著名的“周礼”,也就是周朝的政治文化制度。一般认为“周礼”的制作者是周公旦,而周公旦就是周天子的代表。所以,在周天子政令通行的时代,君主就是“礼、乐”的制定者和裁决者。当君主的政令上下通达之时,就是全天下的安宁之日。孔子在此只是表达了对天下安宁的向往,而并不是倡导周朝的封建制。
[252] 这一章的连锁形式不是《论语》真实的语言特色。当我们查寻《论语》时,发现“天子”这个词并不在孔子的词汇之中。孔子只是提到了“王”。除这一章之外,“天子”在《论语》中只出现了一次,那是《八佾第三》中的“天子穆穆”,这引用的是《诗》中的句子。“陪臣”这个词在《论语》中只此一见。而且,这种表达方式没有出现在与《论语》一样早的其他书中,甚至《孟子》中都没有;它显然是晚出之词。
——译按:在对《论语》的研究中有一种错误倾向,即以某个词语或某种概念在该书中出现次数的多少来说明孔子的思想内容或思想倾向。顾氏曾批评过类似这样的算术式的归纳法,可他在此处也不自觉地用这种不周全的论证方法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
[253] 例如,中国最杰出的和最有鉴赏力的学者之一顾颉刚,在他1941年发表的重要论文《孔子的政治主张及其背景》中,就主要是依据这一章进行了他的讨论。他认识到《论语》其他部分显然与此章不一致,却把这种思想作为讨论的基础。见顾(6),第45—47页。
[254] 关于“正名”这一章,韦利指出:“整个这一章是精心制作的、极其具有文学性的段落,它打上了相对晚期的印记。……后儒的作品提供了许多这种‘连锁’修辞的例子。”(韦利,第172页注[1])他认为这种修辞方式具有西元前4世纪后期的特征,并指出孟子没有提到“正名”思想。韦利认为这一章可能是“荀子或其学派的思想插入(《论语》)的部分”(同上,第21—22页)。
这种情形是相当有可能的。荀子自己写过一篇题为“正名”的精彩的文章。“正名”就是“名称的矫正”(或者如戴闻达所建议的,最好是“术语的正确使用”),这是《子路十三》这一章所讨论的真正的名词。但是,组成《荀子》第22篇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参证孔子的有关思想或《子路十三》这一章,这就说明荀子自己并不知道它。在他的这篇文章中,荀子反复引用《诗经》中的证据。如果有来自《论语》的如此有用的论证,相信荀子是很难忽略的。所以,我们就不必怀疑《子路十三》这一章是荀子插入的。如果他不辞劳苦地做了这种插入的工作,他就会积极地使用他插入的引文。
可是,《子路十三》这一章和《荀子》第22篇却具有相似性。它们都突出了刑罚的作用。戴闻达又指出,二者对“苟”字的使用也很相似,见戴闻达,第245页注[1]。但在《子路十三》这一章中,对刑罚的强调比《荀子》更突出和更独特。所以,这一章似乎是从《荀子》的角度撰写的,但作者却是个更法家式的人物。
有两部法家著作提到了“正名”。《商君书》结尾处有一章几乎讲的是与《子路十三》这一章相同的意旨(《商君书》,第334—335页)。《韩非子》也表述道:“名被矫正之时,事物便安定了。”(《韩非子·扬权》:“名正物定。”)在这两部书中,“正名”以倒置的形式出现,即“名正”。《子路十三》这一章与《韩非子》还有另外一种相似,即这一章开头的句子是:“子路说:‘卫君等待着您去管理政府。’”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早期的传统说法都不认为孔子做过卫国之相,但《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讲的一件轶事的开头是,“孔子相卫”。
韦利认为,《子路十三》此章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是在荀子思想影响下的插入文句。况且这位哲学家的两名最著名的学生是法家人物,而此章又明确地显示出了法家思想的影响。
——译按:顾氏的此番论证显然是不够完善的,亦且有许多误解之处。比如子路所讲的:“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明显是设问语气,并不是叙述事实。另外,“正名”是当时各派哲学共同关心的问题之一。
[255] ——译按:《论语·季氏十六》:“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
[256] 《韩非子·显学》:“夫智,性也。……非所学于人也。”
[257] 这一章影响了对《论语·述而第七》“盖有不知而作之”章的解释。见本书注 。
[258] 《韩非子·显学》:“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
[259] 《史记·秦始皇本纪》;参见包德(2),第21页。
[260] ——译按:《史记·秦始皇本纪》。
[261] 以上史实均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262] ——译按:《史记·秦始皇本纪》“与鲁诸儒生议”。
[263] 沙畹指出了分别来自《诗经》和《尚书》的两个措辞,见《史记》卷二,第142页注[2]和第145页注[5]。需要补充的是,其中的“朝夕不懈”(《史记》第146页)极有似于《诗经·何草不黄》的“朝夕不暇”。“懈”字的被替代,可能是因为要押韵,也可能是由于同一书中出现了两次(《诗·烝民、韩奕》)相似的句子“夙夜匪解(懈)”而类推出来的。
碑文中“举措必当”的头两个字(《史记》卷二,第147页)“举措”,沙畹译作“改正了错误”。这句话明显受到了《论语·为政第二》和《颜渊十二》中“举直错(措)诸枉”的影响。所以,此句应被译为“在提拔和免除官员的时候,他总是正中标的”,这才能更好地与上下文相配合。沙畹未能指出这个暗示或关联,但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像《史记》这样的巨著用典颇多,要把它们全部指出来也不大可能。
[264] 《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265] 《史记·秦始皇本纪》“惑乱黔首”。
[266] 《史记·秦始皇本纪》“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当然,很可能整个谈话都是不足凭信的。不过,从随后发生的事件来看,至少在扶苏的名字与儒学之间有一种传统的联系。
[267] 《史记·陈涉世家》。
[268] 《史记·儒林列传》。
[269] 《史记·儒林列传》;《盐铁论》卷四。
[270] 《史记·儒林列传》。
[271] 《汉书·楚元王传》。
——译按:当指楚元王刘交,汉高祖同父异母的弟弟。
[272] 《史记·儒林列传》。
——译按:当指孔子八世孙孔甲。
[273] ——译注:《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274] 《史记·项羽本纪》:“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
[275] 《汉书·高帝纪》:“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威尔伯(第137页)认为,这种奴隶解放不曾(并且可能是从未)强制执行过。可是,它并不会有损于作为宣传手段的有效性,并且这也才是我们在此所关注的。
[276] 《汉书·高帝纪》:“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是何治宫室过度也!”在一个地方,我略微改动了一处德效骞的翻译。
[277] 《汉书·高帝纪》。
[278] 《汉书·高帝纪》:“(沛公)召诸县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279] 《汉书·高帝纪》。
[280] 《汉书·高帝纪》。
[281] 莱茵伯格,第130页。
[282] 《汉书》(2),卷一,第115页。
[283] 《汉书》(2),第15—22页。
[284] 例如,当他对忠实的谋士审食其失去耐性时,就称他为“竖儒”;见《汉书·高帝纪》。
[285] 《汉书》卷四十三。
[286] 《汉书·高帝纪》:“便于天下之民。”
[287] 德效骞译:《汉书·高帝纪》;参见《汉书》卷四十三。
[288] 汉武帝在位时,许多儒生的经济状况才有了极大的改善。不过,在一位法家高级官员掌权后,曾有过一场辩论。这位官员一再把儒生看成是来自“田间和穷巷”中的人,说他们穷得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见《盐铁论》(2),第77、107、121页。
[289] 《汉书·高后纪》。
[290] 《汉书·文帝纪》:“汉兴,除秦繁苛,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大王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
[291] 《汉书·文帝纪》。
[292] 《汉书》(2),卷一,第216页。
[293] 比较《汉书·文帝纪》中的诏书与《孟子》以下篇章:《梁惠王上》“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章,《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章、“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章和《尽心上》“伯夷辟纣”章。
[294] 《汉书·文帝纪》。人民是因为犯法而成为奴隶的,并且这种状况显然是代代相承的。威尔伯(第134页)怀疑所有的政府奴隶是否会在此时都被解放。
[295] 以上均见《汉书·文帝纪》。
[296] 《汉书》卷四十九。
[297] ——译按:针对英文读者,顾氏在英语原文中径称汉武帝为“武”,为此,他解释道:“一位朋友告诫我说,把汉武帝称作‘武’会使汉学家们感到非常不悦。所以,我要指出一个先例,那就是《论语·子张十九》中的‘文武之道’,把周武王称作‘武’,还有其他一些例子可以列举。”其实,正因为人们习惯上称周武王为“武”,才不应该也把汉武帝称作“武”。所以,译文一律改为汉语通常的称呼。
[298] 《汉书·武帝纪》。
[299]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
[300] 《史记·儒林列传》。
[301] 《史记·儒林列传》。
[302] 详见本书前述所引《论语》、《孟子》、《荀子》中的篇章。此外,在《荀子》出现此种观点的部分中,有两篇——《哀公》和《尧问》——据说是汉儒所加。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从目前的讨论来看,它们便是更有意思的了。
[303] 《论语·子路十三》“诵诗三百”章。
[304] 《盐铁论》(2),第59—61、70—71、87—88页;《汉书》(2),第196—198、301页。
[305] 《盐铁论》(2),第39、76页;《史记》卷一百一十二。
[306] 《汉书·董仲舒传》。
[307] 《汉书·董仲舒传》:“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春秋》:“春王正月。”
[308] 即“正”的双关意义;“正月”就是“头一个月”,“正”也有“正确、纠正”之意;见《汉书·董仲舒传》。
[309] 《汉书·董仲舒传》:“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刑之意与(欤)!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孔子之语见《论语·尧曰二十》“不教而杀谓之虐”。《尧曰》篇几乎可以肯定是后来加入到《论语》之中的,但孔子很可能会讲出这样的话。
[310] 《汉书·董仲舒传》:“考之于今而难行。”
[311] 《汉书·董仲舒传》:“岂惑乎当世之务哉?”
[312] 《汉书·董仲舒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313] 《汉书·董仲舒传》。
[314] 《汉书·董仲舒传》。
[315] 《汉书·公孙弘传》。
[316] 《韩非子》卷十八。
[317] 《汉书·公孙弘传》。
[318] 公孙弘声称(《汉书·董仲舒传》)刑罚在殷代是大量使用的。但是,董作宾(他专注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已有多年)认为殷商时代没有这种传统(1948年3月13日的口头交谈)。可是,在《韩非子》中,殷代的酷刑出现在一则轶话的两种说法之中;见《韩非子》卷九。
[319] 《汉书》(2)卷二,第55—56页;《史记》卷二,第171页;《韩非子》卷十六。
[320] 《韩非子·主道》:“君无见(现)其所欲。……闻而不闻,知而不知。”这一章被怀疑是在汉朝早期补入的,但对我们现在的讨论来讲,这并没有什么关系。
[321] 在这个问题上的更进一步的证据,见《史记》(2)卷三,第557—558页。
[322]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
[323] 《盐铁论》(2),第24页。
[324]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325]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公孙)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有却者,虽佯与善,阴报其祸。”
[326]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327] 《史记·儒林列传》。
[328] 《盐铁论》(2),第63—65页。在此,甚至是儒家学者们都不满意公孙弘的无所成就。
[329] 《盐铁论》(2),第38、40—43、66—67、70—73、112、122—123页;《盐铁论》卷五。众所周知,《盐铁论》这部书并不是那次论辩的确切记录,而是桓宽个人根据当时的记录而撰写的文学作品(《汉书》卷六十六),所以,它应被谨慎使用。不过,它成书于那次事件发生后的几十年间,并且与这个时期的其他材料相比较,它基本上讲的是实情。对它的整体上的权威性,也有人提出过不太严重的疑问,见《盐铁论》(2),xxxix-xli。当我们记起“儒生”公孙弘在策对中使用的法家术语时,就很有理由认为,像桑弘羊这样的官员很可能是被公开认定的法家人物,正如他在《盐铁论》的记载中所表现出的言行那样。
[330] 《史记》卷三,第568—569页。
[331] 《史记》卷三,第558页。
[332] 《汉书》(2),第16、106页。
[333] 《汉书·儒林传》。
[334] 《史记》卷一,Cvi。
[335] 胡(3),第28、34—35页。
[336] 韦利,第241页;冯,第370页。
[337] 见《伪书》,第442—445页;冯,第361—369页;顾(3),第119—121页。
[338] 《礼记》中的《儒行》篇确实亦复如是,还虚构了孔子与鲁哀公之间的对话。“儒”在《论语》中只出现了一次,那是《雍也第六》中的“君子儒,小人儒”,这清楚地说明,在孔子时代,这个词并没有在《礼记》中经常使用的意思。塞进孔子口中的那些陈述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即一位“儒”的缺点不能被当着他的面列举出来,而他则有时拒绝从政,宁愿隐居[《礼记》(2),第405、408页]。这反映了后期儒学的特点。
[339] 比较《礼记》卷一,第138—139页与《论语·述而第七》“子疾病”章和《子罕第九》“子疾病”章。
[340] 比较《礼记》卷一,第136—137页与《论语·先进十一》“颜渊死”章;见崔3.28。
[341] 冯,第43页;梅,第182页;《史记》卷五。
[342] 常镜海,第8页。
[343] 以上详见沙畹翻译的《史记》之注释,以及崔,卷一、卷二;钱穆,第42—45页;威廉,第76—84页。
[344] 比较《论语·先进十一》“子不语怪力乱神”章与《史记》卷五,第310—315、330、349—351、352—353页。
[345] 《史记·孔子世家》:“要盟也,神不听。”这个故事在《孔子家语》卷五中稍有变动。《史记》的这种说法有两个缺点。第一,它违背了孔子所主张和实践的讲求良好信用的原则;第二,它强调了超自然的赏罚。这些与我们所知的孔子都不相同。
[346] 崔,卷二。
[347] ——译按:顾氏在此处对于《孔子世家》的批评确实很有道理,但有时也未免言之失苛。如“席不正,不坐”之类,虽然不能说是孔学的精华,但也并不是不合史实的。
[348] 钱穆,第37—38、42页。
[349] 戴闻达(3),第333页。关于整个《史记》被插入的问题,见杰戈尔。
[350] 崔,卷一;参看卷四。
[351] 《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之要旨”。
[352] 德效骞(他对《汉书》的翻译使他对这一时期相当熟悉)断定司马迁是道家人物(《汉书》(2)卷二,第346页)。沙畹尽管反对这种看法,却引用了支持这种看法的一些早先的观点。他用来反对这种看法的唯一事实是,司马迁对孔子进行了公开的赞誉(《史记》卷一,xlix-1)。可是,沙畹在后面的两页中说道,司马迁写了“一部讽刺作品”。
[353] 正如沙畹所坚持的,即使这篇传记的最后一段(对孔子的公开赞誉)是司马迁所写(《史记》卷一,1和注[1]),也不能证明这篇传记之中的一大部分不可能由他父亲写成。
[354] 《史记》卷五,第299—301和第299页注[4];《庄子》卷一,第338—340、357—358页;《庄子》卷二,第46—49、63—66页。对这次内含其他用意的会谈的批判,见崔,卷一;钱穆,第4—8页;达布斯(3),第216页。
[355] 《史记·儒林列传》。
[356] 《史记》卷三,第558—559页。
——译按:《史记·平准书》:“当是之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
[357] 《史记》卷一,Ⅲ。
[358] 《史记》,Ⅶ-1。
[359] 《史记》,Ⅲ。
[360] 《史记》卷五,第434—435页注[1]。
——译按:当指《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361] 见《盐铁论》书中各处;《汉书·公孙弘传》。班固在概括汉武帝的成就时,也用冷淡的称赞表示了贬责。见《汉书·武帝纪》。
[362] 《汉书·夏侯胜传》:“亡德泽于民。”
[363] 《盐铁论·褒贤》:“庶几成汤、文、武之功,为百姓除残去贼。”《论语·阳货十七》:“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364] 《钦定春秋》,皇帝之序,第16—46页。
[365] 《钦定春秋》,26.21b—22a、27.30a。
[366] 威特福格尔,27—28页;克拉克,第121页。
[367] 威特福格尔,27—28页;克拉克,第121页。
[368] 朱,第295页。
[369] 麦考利,第333—334页。
[370] 布伦蒂埃,第199页。
[371] 勒费弗尔,Vi。
[372] 勒费弗尔,第50页。
[373] 勒费弗尔,第215页。
[374] 论卫励,第108页。
[375] 莱布尼兹,Praefatio(3)。
[376] 伏尔泰,xlix,第284—285页。
[377] 巴杰尔,导论,第95—96页。
[378] 魁奈,第636页。
[379] 见邓恩和罗博瑟姆。
[380] 皮诺特,第257页。
[381] 引自赖克韦恩,第78页。
[382] 伏尔泰,xxi,第220—221页。
[383] 引自邓恩第125页对利玛窦的评论;亦见特里高尔特,第157页。
[384] 伯纳德,卷一,第324页;参见伯纳德,第157页。
[385] 伯纳德,第325页;参见罗博瑟姆,第64—65页。
[386] 胡(6),第30页。
[387] 以上见朱,第113、135页。
[388] 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这个学派并不认为宋代儒家学者对古典的注释是理解早期儒学的标准,所以,他们要返回到汉代儒家学者的注释之中去。
[389] 邓恩,第154—159;伯纳德,卷一,第135页;《杰出的中国人》卷一,第422—423页;朱,第99—153、166—169页;张荫麟,第66—68页。
[390] 胡(6),第70页。
[391] 许,第30—31页。
[392] 皮诺特,第183—185页。
[393] 例如,关于这一时期耶稣会士作者们的报告,可见特里高尔特,第136—175页;以及杜霍尔德,卷三,第14—63页;亦见邓恩,第89—91页。伯顿在他的《沉思的分析》中报告说:“耶稣会士利玛窦告知我们”说,“他们(中国人)是所有民族中最迷信的”。(伯顿,第310页)
[394] 伯纳德,第334页。
[395] 邓恩,第92页。
[396] 赖克韦恩,第78页。
[397] 《论语·卫灵公十五》:“辞,达而已矣。”
[398] 赖克韦恩,第77页。
[399] 伏尔泰,xlix,第271页。
[400] 伏尔泰,xvi,第335页。
[401] 赖克韦恩,第80页。
[402] 伏尔泰,xlix,第272页。
[403] 费内隆,第43页。
[404] 孟德斯鸠,卷一,第142页。
[405] 《百科全书》卷三,第347页。
[406] 李明,第242页。
[407] 见傅路德。
[408] 见伏尔泰,xvi,第330—333页和孟德斯鸠,卷一,第142—144页。卡尔卡松精彩地分析了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论述,指出他着重关切的是维持某些与中国不相干的先入之见,并讨论了怀疑耶稣会士之报告的整个问题;见卡尔卡松。
[409] 拉奇,第96—97页。
[410] 哈特斯利,第143页。
[411] 贝德,第286页。
[412] 朗松,第413页。
[413] 在上述引文中。
[414] 在另一个标题之下;见“参考书目”中的“费内隆”条下。
[415] 朗松,第5—28页。
[416] 朗松,第24—25页。
[417] 拉奇,第4—5、140页;赖克韦恩,第20页;以及“参考书目”中“皮诺特”条下的第458—466页。
[418] 皮诺特,第15—16、141—142页。
[419] 朗松,第411—412页。
[420] 朗松,第420页。
[421] 例如,见珀切斯,第387页。
[422] 特别是:朱、赖克韦恩、皮诺特、马弗里克、赫德森、论卫励和罗博瑟姆。
[423] 拉奇(2),第440—441页和注[17];赖克韦恩,第85页。
[424] 皮诺特(2),第213—214页;马弗里克,第44—58页。
[425] 比较《论语·子路十三》“叶公问政”章;李明,第125页;以及狄德罗:《百科全书》,ix,第357页。
[426] 孟德斯鸠,卷一,第346—350页。
[427] 林赛,第128页。
[428] 见《诗》(2),第255页(《诗经·大雅·皇矣》);《书》,第454—458、495—502页(《尚书·多方、多士》);《论语·子路十三》“苟正其身”章、《宪问十四》“卫灵公之无道”章;《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汤放桀”章。
[429] 杜霍尔德,卷二,第18页;林赛,第572—573页;戈德史密斯,卷一,第181页。
[430] 孟德斯鸠,卷一,第144页。
[431] 李明,第284页。
[432] 拉斯基,第80页。
[433] 皮诺特,第395页。
[434] 珀切斯,第387页。
[435] 杜霍尔德,卷三,第12页。
[436] 伯顿,第503页。
[437] 巴杰尔,第91—97页。
[438] 戈德史密斯,卷一,第137—141页。
[439] 伏尔泰,xvi,第335页;马弗里克,第30、49、201、235页;波伊沃里,第160—161页。
[440] 论卫励,第135页。
[441] 钦纳德,第75页。
[442] 例如,可见由波伊沃里(第138—140页)指出的广东地区的令人惊讶的繁荣程度。这样的观察报告在当时是很普通的。
[443] 伏尔泰,xvi,第109—110页。
[444] 皮埃尔·贝尔是那些为法国大革命铺平道路的思想家当中的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对伏尔泰和《大百科全书》的编者狄德罗有极大的影响。他是在一所耶稣会的学院里受教育的。他的重要的《批评史辞典》包含了一些有关中国的资料。朗松写道:“如果贝尔能够不仅没有诽谤而且不带荒谬地主张,一个无神论者的社会能够维持自身,并且还像任何基督教社会一样井井有条的话,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怪论,此怪论依据以下事实而具有了权威性,即传教士观察到了或者据信是他们观察到了,中国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它管理完善并且具有所有的美德;而它的统治集团——文人学士(士大夫)——都是无神论者。”(朗松,第18页)
[445] 伏尔泰,xvi,第111页。
[446] 巴杰尔,第91页。
[447] 引自赖克韦恩,第81页。
[448] 科克,第44页。
[449] 韦勒斯,第351页。
[450] 皮诺特(2)。
[451] 例如,见李明,第241—311页;杜霍尔德,卷二,第115—123页;伏尔泰,xvi,第330—333页和xxi,第211—214页。亦见赖克韦恩,第102—103页。
[452] 马弗里克,第127页。
[453] 魁奈,第564页。
[454] 魁奈,第656页。
[455] 费伊,第343页。
[456] 费伊,第342页。
[457] 费伊,第415页。
[458] 费伊,第343—344页。
[459] 科克,第178—185页。
[460] 柏林顿,卷二,第11页。
[461] 科克,第72页。
[462] 为便于比较,我把这些观点用数字编了号。孔子的观点在《论语》的以下章节:(1)《述而第七》“子不语”章;(2)《先进十一》“季氏富于周公”章;(3)《雍也第六》首章和《述而第七》“自行束脩以上”章;(4)《雍也第六》“人之生也直”章、《子罕第九》“子欲居九夷”章和《子路十三》“樊迟问仁”章;(5)《阳货十七》“宰我问”章。杰弗逊的观点见以下科克的:(1)第114页;(2)第174页;(3)第133页;(4)第116—119页;(5)第145页。
[463] 杰弗逊,卷一,第446页。
[464] 杰弗逊,卷四,第425页。
[465] 这个概括是原初提案中的一部分,还有些是来自于杰弗逊《弗吉尼亚笔记》的叙述。见杰弗逊,卷二,第220—229页和卷三,第251—255页。
[466] 杰弗逊,卷四,第426页。
[467] 伏尔泰,xxi,第212页。伏尔泰补充道,这些官员都是“投票选举的”,这当然是错误的,但却可能增强了杰弗逊的兴趣。因为在那时他读了这本书并作了笔记(《道德习俗随笔》);见杰弗逊(2),第14页。
[468] 邓嗣禹把出版在1775年之前的11本英文书和3本法文书列在他的“叙述中国科举制度的西方著述目录”中;见邓,第308—312页。这个列举并未自称是详尽无遗的。
[469] 在老国会图书馆被焚毁后,杰弗逊在1775年把他的个人图书馆卖给了国会,其目录在《美国图书馆目录》中,这是由乔纳森·埃利奥特印行的(华盛顿,1815年)。其中列举的两本书(但没有详细说明版本,同上,第10、120页)公正全面地说明了科举制度,它们是杜霍尔德(卷三,第1—14页)和李明(第280—283页)。杰弗逊也有后者的法文版。对于前者,在他卖出的图书馆中只有其中的第一卷,所以,不能确定他是否曾有过第三卷。
[470] 杰弗逊,卷八,第221页。
[471] 杰弗逊,卷四,第494页。
[472] 杰弗逊,卷四,第428页。
[473] 杰弗逊,卷五,第95页。
[474] 杰弗逊,卷四,第501页;卷五,第51页;阿罗伍德,第129—131页;杰弗逊(2),第49—52页。
[475] 见邓。
[476] 邓,第306页。
[477] 胡,第200页。
[478] 许,第30—31页。
[479] 孙逸仙,卷一,《民权主义》,第10页;(2),第169页;(3),第232—234页。《三民主义》的译本根据的就是这三本书,我没有依从任何单独的译本。很多(已出版的)孙氏著作的译本是不太令人满意的,并且有时还有误解。原因之一是,大部分材料当初都是发表的讲演,很难翻译得既合乎原意,又明白易懂。关于孙氏把孔子看作是坚持民主思想的章节,见孙中山,卷二,《民生主义》,第44页;(2),第444页;(3),第476页。孙中山,卷二,《民权初步》,第104页。
[480] 孙逸仙,卷一,《民权主义》,第10—11页;(2),第170页;(3),第236页。
[481] 孙逸仙,卷二,《民族主义》,第52页;(2),第98页;(3),第158—159页。
[482] 孙逸仙,卷二,《民族主义》,第66、70页;(2),第125—126、133—134页;(3),第186、194—195页。
[483] 莱茵伯格,第193页。
[484] 孙逸仙,卷二,《民生主义》,第15—16页;(2),第390—391页;(3),第429—430页。
[^485] 孙逸仙,卷二,《民生主义》,第16页;(2),第391—392页;(3),第430页。
[486] 霍尔库姆(2),第435页。
[487] 孙逸仙,卷二,《民权初步》,第99—112页。
[488] 孙逸仙,卷二,《民权初步》,第106—107页。
[489] 孙逸仙,卷一,《民权主义》,第100—112页;(2),第340—360页;(3),第383—400页。
[490] 孙逸仙,卷一,《民权主义》,第109—110页;(2),第356—358页;(3),第397—398页。
[491] 见《论语·为政第二》“哀公问”章、《雍也第六》首章、《述而第七》“自行束脩”章、《先进十一》“子路使子羔为费宰”章、《颜渊十二》“樊迟问仁”章、《宪问十四》“子言卫灵公之无道”章、《卫灵公十五》“子曰已矣乎”章。
[492] 孙逸仙,卷一,《民权主义》,第36页;(2),220页;(3),第281页。
[493] 孙逸仙,卷一,《民权主义》,第36页;(2),第221页;(3),第282页。
[494] 孙逸仙,卷二,《建国方略》,第3页。
[495] 孙逸仙,卷一,《民权主义》,第110页;(2),第358页;(3),第398页。
[496] 莱茵伯格,第24页。
[497] 林(2),第2页。
[498] 《纽约时报》(纽约),1948年4月27日,第12页。
[499] 孙逸仙,卷二,《民族主义》,第52—53页;(2),第98—99页;(3),第159—160页。所引的一章明显出现在《大学》之中(《礼记》,卷二第411页),尽管孙氏用“平”代替了“明明德于”。
跋
通过本书的述说,我们认为,孔子这位出身微贱的鲁国人,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取得过很可观的实际政治成就。我们也看到,孔子死后,他的影响却在不断增长,直到那些敌视他的原则的人们不得不依靠歪曲、滥用这些原则的方法来进行自卫。然而,他们到头来也不过是部分地取得了一些成功。
多少个世纪以来,孔子的名字受到了许多民族的人们的欢呼。尽管我们在本书只是作了概括性的研究,但还是了解到,孔子的思想虽然屡遭人们的大肆窜改,仍然在各种类型的文明史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对这些事实的反思,我们不可能不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孔子的影响引人注目地持久不衰?既然孔子首要关切的是社会实际和政治哲学,所以,原因可能就在这些领域中。
就其最宽泛的意义而言,国家的政治体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独裁(极权)的和民主的。不用说,每一种类型都有各种表现形式,当然也有这两种类型的结合。在独裁国家中,权力绝对属于一个人或一伙人,而大部分人民不能有效地分享权力。在民主国家,权力绝对属于全体人民。在独裁政府的统治下,政府的目的是实现通常所说的“国家利益”,因此就可以牺牲大多数公民的福利和幸福。相反,真正的民主必须关切每个公民的福利和幸福,因为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一员。
历史证明,真正的和有效的民主政治是一种很难完全实现的政治形态,而要想把这种形态永久地保存下去,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相比较而言,独裁主义却在茁壮成长。这是有一定原因的。在独裁政治的统治下,国家的哲学和个人的义务是由政府相对明确地加以规定的。可是,在民主政治中,国家没有哲学(除非它指的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个人的义务也不完全清楚。可以说,他可以支持政府,也可以反对政府,这是由他的良知所决定的,并没有别的外在强制力。
可是,有许多人以种种雄辩的手段渴望告诉民主政治中的某位公民什么是他的义务。这位公民会以怀疑的态度注视着那些如此热情地对他做思想工作的人们。这种表现是相当正确的。无论如何,他将面对困难的选择。具体来说,他将把国家的命运委托给那些诚实与否令人怀疑的专业政治家呢,还是那些心地善良但政治技能却不太老练的业余人士呢?
进而言之,这其中甚至有一个更大的两难。在民主政治中,绝对的权威属于全体人民,但是,广大人民通常在政治领域连业余水平都达不到。因为,一个业余者肯定得是个“爱好者”,而民主政治中的公民们却并不总是乐于参与实际的政治程序。他们对政府越是满意,越是缺乏实际参与的兴趣。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一个良好的民主政府就是它自己的最大敌人。也就是说,当它的公民放松警惕时,总是会出现以下危险:民主的敌人可能接管政府。
民主政治也会面临更为难解的思想上的两难。与孔子相一致的政治哲学家们认为,在一个协作性的国度里,人民必定对他们的政府有信心。 [1] 进而言之,既然所有的人必须在决定政府的目的甚至是措施上发挥一定的作用,那么,他们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赞同这个社会的基本政治哲学。然而,民主政治既不能给它们的公民规定这样的哲学,也不能宣称有任何一种这样的信念:这种政治形式或政治体制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批评,也不能成为讨论的主题,更不能受到怀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种种民主政治也总是,并且必定总是,受到独裁主义宣传家的攻击。针对这种情况,民主政治必须保护自己,然而却不能够禁止诉诸理性的自由言论。
并不是每个赞成把民主作为抽象原则的思想家都能够为它提供一种前后一贯的哲学,以满足它的相当苛刻的要求。孔子哲学则在一种不同寻常的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并且被认为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而使他的思想得到了如此广泛的赞成和共鸣。如果说孔子哲学在完全现代的意义上是民主的,这种说法将是大错特错的。然而,并非大错特错的说法是,孔子是民主的先驱,他在旷野里大声疾呼,传布着大道。所以,我们所要叙述的核心内容是,孔子欣赏某些基本的政治原则,这些原则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精诚协作。正是这些原则才使得其他哲学家很难超过孔子,甚至并不总是能赶得上他。孔子并不仅仅是赞同协作性的国家,他还满腔热情地献身于这种国家的实现。他为民主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而且还有呐喊助阵。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把彻底的热情与审慎的中庸之道相结合,在号召人们献身于民主事业的同时,不要做出过度的断言,以免损害这一事业的逻辑完整性。
孔子似乎意识到,民主所面临的最艰苦的战斗不是与罪恶的激烈对抗,而是在个人内心深处所进行的反对无聊懒散的静悄悄的战斗。独裁主义用虚张声势和允诺对所有难题的最终解决来诱惑人们,而民主政治只能提供简朴的人的尊严和不停歇地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机会,并且是除了不断工作的机会之外没有任何奖赏。从来都不曾发生过一场民主的最后决战,也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民主政治的最高目标也不能是(在静态的完善意义上的)一个完美的国家形式或完善的政治体制,因为那种认为事物会停止变化的想法是一种幻觉。民主政治只希望培养出这样的人,他们有能力有效地应对种种新的情势。
孔子似乎认识到,假如说为了指导社会,一定要建立起不可变更的标准,无论它是形而上学体系,还是书本、法律的,或者仅仅是原则性的,都会有三重危险。首先,它窒息了创发性。其次,当出现了立法家预料不到的情势时,它可能会造成伤害。最后,如果批评(这在一个协作性的社会里是不能被压制的)摧毁了人民的信仰,他们会无所适从。孔子并不想把任何绝对的权威强加于人。
然而,如果国家不想坠入无政府状态,某种权威还是要有的。不过,孔子情愿把这种权威托付给某些人,但不是任意的人,而是恪守大道之人。可是,这个大道并不是僵硬的规则,也与形而上学无甚关系。它是一整套思想,需要人们把它创制出来并加以不断发展。“人们能扩展大道,但是,大道(自身)不能扩展人。” [2] 与之相似的是当今所谓的“民主的生活方式”,只不过孔子是以现代民主所不常有的更大的热情和热诚去倡导它罢了。因为孔子明白,没有这种热情,协作社会是不可能到来的。
孔子对人们是抱有信心的。不是所有的人,因为他并不是那么天真的。但他相信大多数人是诚实的。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从政。可是,他的确在倡导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一定的教育,使他们真正成为协作社会的成员。他还提议,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应该受到进一步的教育,并让他们得到政府机构的位置。做到了这一步,他情愿允许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最佳判断治理国家。他还相信,全体人民最终会有能力对善恶之官员做出区分的。
孔子确信人类能走到这一步。
注释
[1] 《论语·颜渊十二》“子贡问政”章。
[2] 《论语·卫灵公十五》:“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附录《论语》的可靠性
所有学者一般来说都同意以下观点:尽管《论语》的某些部分是可以商榷的,但这部书总的来说还不失为我们研究孔子的最佳的和独一无二的资料来源。这种全体一致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论语》这本书未在早于汉代的任何著作中被点名提到过。可是,它的一些章节却明显地出现在了早于汉代的一些著作之中, [1] 并且有证据表明,现存《论语》中的一些词句在某个时期在儒家集群中相互传承,而使用者对它们到底来自于哪本书却没有特别点明。
《论语》中孔子所说的那些话到底是他什么时候讲述的,以及什么时候他的弟子们首次把这些话编纂成书,这些都是难以确定的。首次编辑整理这些话语的可能不是孔子的直传弟子,而是其直传弟子的某些弟子。有人认为,现存《论语》的前10篇正是当初那本书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的5篇是在后来的某个时候增补的。可以肯定崔述的推测是正确的,这就是,从第16篇到第20篇的最后5篇是更晚些时候增补的。在最后这5篇中,孔子通常被直呼为“孔子”而不是“子”,并且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同也使它们与前面的篇章区分开来。 [2] 不过,说最后5篇是后加的,并非意味着它们之中的材料就没有早期的。《论语·学而第一》“巧言令色”章就一字不变地重现在《阳货十七》中,这就证明了最后几篇之中也有早期的材料。《子张十九》总的来说只与孔子弟子而不与孔子本人有关,它与那些最早的篇章一样可靠。可是,正如下文将要讨论的,在最后5篇中,可疑材料的比率是相当之高的。
西汉时期据说有3种《论语》的版本。西汉末年前后,一位名叫张禹的学者依据其中的两种版本制作了一个新的版本(《张侯论》),此后,这个版本变得很流行,以至于其他版本就逐渐湮没不见了。 [3] 大约在175年,《论语》的这个版本被刻在了石碑上,这个石碑文本的部分残片至今犹存。尽管这些残片显示出与现存版本的《论语》有些不同,但这些不同大部分是无足轻重的,并没有严重影响到它的文意。 [4]
有内在的证据表明,《论语》是一部早期著作。高本汉发现,《论语》与《孟子》有着“相当一致的语法体系”,他还把那些次要的不同作为根据,来把《论语》解释为是比《孟子》更早一些的文本。 [5] 《论语》之中没有某些概念,比如(形上意义上的)“天”和“地”,以及“阴阳”和“五行”,所以,这些概念无疑是最早出现在周朝末年或者汉代作品中的。 [6] 《论语》所描述的孔子并不是个超人一般的圣人,而是一位平易近人和通情达理的凡人。他没有如在后来的传奇中那样被抬高,也未被夸大说曾担任过极其重要的官职。他有疑虑和怯懦,也有信心和勇气。
《论语》所具有的可靠性的最佳证据之一是如下事实:尽管《论语》明显是一本儒家之书,但却包含了许多儒生们认为不应该有的东西。《子张十九》详述了弟子之间的思想分歧和争论,“陈子禽谓子贡”章还告诉我们,有人说孔子比不上弟子子贡。《雍也第六》“子见南子”章还说孔子会见了声名狼藉的南子,这些都使无数的过分拘谨的儒生颇为受窘,而且在汉代还被他们的敌人用来挖苦他们。 [7] 然而,这些东西并未被从《论语》的文本中删去,这无疑增加了我们对这本书的尊重。
不过,《论语》也有一些成问题的章节,从纤微的令人怀疑之处到明目张胆的伪造。《乡党第十》提出了特殊的难题,马伯乐和阿瑟·韦利认为这一篇论述的是种种礼仪问题,讲的是理想的君子应该具有的举止行为,并且是被作了某种改编之后插入到《论语》之中的。 [8] 这种论断是相当真实的,我们确实不能毫无疑虑地把这一篇的所有章节都看成是描述了孔子本人的行为。可是,其中的一些章节,像首章、“康子馈药”章和“厩焚”章,明确点出了孔子之名,显然指的是孔子的行为;还有一些章节是特指个人的行为,大概指的也是孔子。
有一些章节与孔子和他的弟子都无关系,这是不相干的插入,计有《季氏十六》“邦君之妻”章、《微子十八》“柳下惠”章和最后三章,以及《尧曰二十》首章。 [9] 汉代石碑上的《论语》明显缺少《尧曰二十》的末章,据说在《鲁论语》中也没有这一章, [10] 而据信《鲁论语》是个最好的《论语》早期版本。我曾叙述过对于《为政第二》“吾十有五”章(见本书注 )和《子罕第九》“凤鸟不至”章(见原书第202页)的怀疑。崔述提出对《卫灵公十五》首章的疑问,依据很好的理由,他认为此章是缺乏依据的。 [11] 韦利怀疑《季氏十六》首章, [12] 这个怀疑是很可以成立的。在这一章,子路和冉求一同侍奉于季氏,而孔子却好像是说冉求掌握着鲁国的主要权力。可是,子路显然是在冉求之前做的季氏宰,而像子路这种脾气的人会在被贬职之后仍然侍奉季氏,确实是大有疑问的。 [13] 还有几章反映了道家思想,对它们一定得有保留意见;它们是《宪问十四》“贤者避世”章到“子击磬于卫”章、《季氏十六》“隐居以求其志”章、《阳货十七》“予欲无言”章(见本书注 )和《微子十八》“楚狂接舆”章到“逸民”章。 [14]
在最后5篇中,有9章所引述的孔子的话语明显以一种非常学究的方式使用了数字,它们讲到了三种错误(“三愆”)、九种关切(“九思”)和四种不良品质(“四恶”)等。它们是《季氏十六》“益者三友”章到“君子有三畏”章和“君子有九思”章、《阳货十七》“子张问仁”章和“由也”章,以及《尧曰二十》“子张问”章。在前15篇中,孔子并未以此种方式讲说过。《公冶长第五》“子谓子产”章和《宪问十四》“君子道者三”章只是明显的比拟,与过分看重数字的做法是不同的。《孟子》也没有此种情形。尽管这些章节中的有些内容源自孔子,但很可能是被后世儒学中的教条主义作风重新定了型。
最后,有6章看起来有待查明其事实,它们讲的是孔子的遭遇或哲学。我们有必要怀疑它们是被伪造后加入文本之中的,因为在其他地方有与之相反的证据。这6章分别是:《述而第七》“加我数年”章(见原书第201页)、《子路十三》“子路曰卫君”章(见本书注 )、《季氏十六》“天下有道”章(见原书第220页)和“生而知之”章(见原书第221页)、《微子十八》“齐景公待孔子”章(见本书注 )和“齐人归女乐”章(见本书注 )。
注释
[1] 这种出现列举在理雅格,卷一,第17—18页。
[2] 崔述对《论语》的批判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学者对此论题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它包含在“参考书目”中的崔、崔(2)和崔(3)之中。他的结论概述在崔(3),第24—35页。我曾很详细地概括过这个文本的历史,见顾立雅(5),卷二,第9—20页。亦见钱穆(2)。
——译按:正如顾氏所言,孔子的直传弟子称孔子为“子”,而再传弟子则称孔子为“孔子”,因为他们称自己的老师为“子”。《论语》中“孔子”与“子”并存,就说明是由孔子的直传弟子和再传弟子经过多次编辑整理而成的。我们很难确定每次整理的时间和程度,但不能断然否定孔子的直传弟子与《论语》成书的直接关联。
[3] 《汉书·张禹传》;崔,卷二;崔(2),卷三。
[4] 这些残片复原后的出版文本见张国淦,第44—46页;以及罗(3)。
[5] 卡尔格伦,第24—35页。
[6] 关于这些概念后来出现的日期,见本书注 、注 、注 。
[7] 《盐铁论》(2),第72—73页。
[8] 马伯乐,459;韦利,第55页。
——译按:《论语·乡党第十》所描述的,应该是孔子的行为和行为准则。只是有些情景的存在是需要相关条件的,而孔子的一生并不是时刻都具备此类条件。换句话说,只要条件允许,孔子肯定是依照这一篇所陈述的规则行事的。而事实上,这一篇所描述的情景,在孔子身上都是发生过的。
[9] ——译按:这样的章节也不能断然说与孔子或其弟子无关,因为还有一种可能,即它们是一些残缺的章节,在流传过程中佚失了诸如“子曰”之类的文字。
[10] 《论语二十章勘稽》,卷三。
——译按:1973年,在河北定州出土的西汉中山怀王刘修的墓葬中发现了一部残损的竹简本《论语》,据有关专家研究,这是《鲁论语》的一个抄本,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论语》抄本。在这个抄本上就有《尧曰二十》的前两章。这个抄本经初步整理,由文物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对它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即使撇开这个发现不谈,顾氏关于《论语》可靠性的一些判断还是比较草率和片面的,只能作为研究相关问题的参考,而不能视为深思熟虑的定论。
[11] 崔,卷三。
[12] 韦利,第204页注[6]。
[13] ——译按:子路离开鲁国,更有可能是追随辞职的孔子周游列国,而并不是被免职,因为对于这一事件并没有明确记载。孔子结束周游列国之后,子路也曾在鲁国,他与冉求同见孔子,亦有可能。孔子晚年,冉求做季氏宰,而季氏几乎完全控制了鲁国,说冉求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鲁国的权力,也是可以成立的。
[14] ——译按:孔子周游列国,与隐士或具有道家思想倾向的人士相遇甚至相往还,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论语》记载此类事件,也属正常,未必尽是道家的侵入。
参考书目
以下所列著述是原书引用或提及的。前面是它们的缩写(简写)形式。中译本按英文字母顺序重新编排了它们的次序,以便检索。
A
阿特休勒 Ira M. Altshuler, M. D. , "The Part of Music in the Resocializ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in Occupational Therapy and Rehabilitation XX (Baltimore, 1941), 75-86.
《音乐在精神病人康复过程中的作用》
阿罗伍德 Charles Flinn Arrowood, Thomas Jefferson and Education in a Republic (New York and London, 1930).
《托马斯·杰弗逊与共和国的教育》
埃斯卡拉 Jean Escarra, Le Droit Chinois (Peking and Paris, 1936).
《狄德罗论中国》
B
巴杰尔 Eustace Budgell, A Letter to Cleomenes King of Sparta (London, no datebut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ue gives, 1731).
《写给斯巴达的克莱奥门尼斯的一封信》
《百科全书》 Encyclopedie, ou Cictionnaire Raisonne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etiers, ed. By Denis Didcrot and J. L. d' Alenbert, Vols. III and IX (Paris, 1753 and Neufchastel, 1765).
《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
贝德 Jean-Albert Bede, "Guatave Lanson," in The American Scholar, IV (New York, 1935), 286-291.
《古斯塔夫·朗松》
贝尔纳斯 James F. Byrnes, Speaking Frankly (New York, 1947).
《直言不讳》
本田 Honda Seishi,《作易年代考》,载《先秦经籍考》,江家安译(上海,1933),上册,39-66。
毕瓯 Edouard Biot, Essai sur l' Histoire de l' Instruction Publique en Chine, et de la Corporation des Lettres (Paris, 1847).
《中华民国教育史论文集》
伯纳德 Henri Bernard, S. J. , Le Pere Matthieu Ricci et la Societe Chinoise de son temps (1552—1610), 2 vols. (Tientsin, 1937).
《利玛窦神父与(1522—1610)中国社会》
伯纳德(2) Henri Bernard, S. J. , Sagesse Chinoise et Philosophie Chretienne (Tientsin, 1937).
《聪慧的中国人与理性的基督徒》
伯恩斯 C. Delisle Burns, Democracy, Its Defects and Advantages (New York, 1929).
《民主及其优劣》
伯恩斯(2) C. Delisle Burns, Challenge to Democracy (New York, 1935).
《民主的挑战》
伯顿 Bobert Burton, 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1621; reprinted New York, 1938).
《沉思的分析》
伯希和 Paul Pelliot, "Meou-tseu ou les doutes leves." in T' oung Pao, XIX (Leyden, 1920), 255-433.
《〈墨子〉置疑》
柏林顿 Vernon Louis Parrington,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3 vols. (New York, 1930).
《美国主流思想》
柏拉图 Cratylus, in The Dialogues of Plato, tr. by Ben jamin Jowett, 2 vols. (1892; reprinted New York, 1937) I, 173-229. (Pagination given, forthis and the following dialogues, as in Stephens).
《柏拉图对话集》
柏拉图(2) Phaedo, in ibid. I, 441-501.
《斐多篇》
柏拉图(3) The Republic, in ibid.I, 591-879.
《共和国》
柏拉图(4) Laws, in ibid. II, 407-703.
《法律篇》
包德 Derk Bodde, China's First Unifier (Leyden, 1938).
《中国的第一位统一者》
包德(2) Derk Bodde, Statesman, Patriot and General in Ancient China (New Haven, 1940).
《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和将军》
布伦蒂埃 Ferdinand Brunetiere, Etudes Critiqusesuri' Histoire de la Litterature Francaise, 8 serie (Paris, 1907).
《法国文学批评史》
布赖斯 James Bryce, The Holy Roman Empire, 8th ed., rev. (London and New York, 1897).
《神圣罗马帝国》
C
常镜海 常镜海:《中国各派历史思想》,载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LX (Shanghai, 1929), 1-19。
陈启天 陈启天:《韩非子校释》(上海,1940)。
陈梦家 陈梦家:《五行之起源》,载《燕京学报》第24期(北京,1938),35-53。
崔 崔述:《洙泗考信录》,载《崔东璧遗书》,顾颉刚编,八卷本(上海,1936),卷三。
崔(2) 崔述:《洙泗考信录余》,载《崔东璧遗书》,卷四。
崔(3) 《论语余说》,载《崔东璧遗书》,卷五。
D
德效骞 Homer H. Dubs, "Did Confucius Study the' Book of Changes'?" in T’oung Pao, XXV (Leyden, 1928), 82-90.
《孔子研究过〈易经〉吗?》
德效骞(2) Homer H. Dubs, "The failure of the Chinese to Produce Philosophical Systems," in T’oung Pao XXVI (Leyden, 1929), 98-109.
《中国人创制哲学体系的失败》
德效骞(3) Homer H. Dubs, "The Date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Philosopher Lao-dz,"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LXI (Baltimore, 1941), 215-221.
《哲学家老子的时代》
戴 戴望:《戴氏注论语》(1817)。
戴闻达 J. J. L. Duyvendak, "Hsun-tzu on the Rectification of Names," in T' oung Pao XXIII (Leyden, 1924), 221-254.
《荀子论“正名”》
戴闻达(2) J. J. L. Duyvendak, "The Chronology of Hsun-tzu," in T' oung Pao, XXVI (Leyden, 1929), 73-95.
《荀子年表》
戴闻达(3) J. J. L. Duyvendak,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Cult of Confucius. By Johm K. Shryock." Review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LV (New Haven, 1935), 330-338.
《对孔子之国家崇拜的起源和发展》
邓 邓嗣禹:《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载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II (Cambridge, 1943), 267-312.
邓恩 George H. Dunne, S. J. ,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ays of the Ming Dynasty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44).
《明末中国的耶稣会士》
董 董作宾:《殷历谱》(Li-chuang Szechwan, 1945)。
杜霍尔德 J. B. Du Halde, S. J. ,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tr. by R. Bookes, Vol.I (London, 1741).
《中国通史》
E
ESS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d. by Edwin R. A. Seligman and Alvin Johnson, 15 vols (1930-1935;reprinted New York, 1937).
《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F
费伊 Bernard Fay, Franklin, the Apostle of Modern Times (Boston, 1929).
《富兰克林,现代的使徒》
费内隆 Franc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enelon, Dialogues des Morts, first published at Cologne in 1700 as Dialogues divers entre les cardinaux Richelieu et mazarin et autres (Paris, 1819).
《死者的对话》
芬纳 Herman Finer, The Future of Government (London, 1946).
《未来政治》
冯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哲人的时代》,Derk Bodde译(北平,1937)。
冯(2) 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载《古史辨》卷二,194-210。
冯(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补》(上海,1936)。
伏尔泰 Oeuvres Completes de Voltaire, 92vols. (Impr. de la Societe Litteraire-ty-pographique, 1785-1789).
《伏尔泰全集》
傅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长沙,1940)。
傅路德 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 ien-lung (Baltimore, 1935).
《乾隆的文字狱》
G
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 (Goteborg, 1926).
《〈左传〉的可靠性及其特点》
高本汉(2) Bernhard Karlgren, "Huai and Han," in Bulletin of the Museum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XIII (Stockholm, 1941).
《淮与汉》
戈德史密史 Oliver Goldsmith,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2 vols (1762; reprinted London, 1790).
《世界公民》
《古史辨》 顾颉刚编:《古史辨》,七卷本,1-5卷(北平,1926-1935);6-7卷(上海,1938-1941)。
顾 顾颉刚:《论孔子删述六经说及战国著作伪书》,载《古史辨》,卷一,41-43。
顾(2) 顾颉刚:《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载《古史辨》卷二,130-139。
顾(3) 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古史辨》卷三,1-44。
顾(4) 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载《古史辨》卷三,309-367。
顾(5)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载《古史辨》卷七(1),1-64。
顾(6) 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载《古史辨》卷七(3),30-107。
顾立雅 H. G. Creel, 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 First Series (Baltimore, 1937).
《早期中国文化研究》
顾立雅(2) H. G. Creel, "Was Confucius Agnostic?" in T' oung Pao, XXIX (Leyden, 1935), 55-99.
《孔子是不可知论者吗?》
顾立雅(3) H. G. Creel,《释天》,载《燕京学报》18期(北平,1935),59-71。
顾立雅(4) H. G. Creel, The Birth of China (London, 1936; New York, 1937).
《中国的诞生》
顾立雅(5) H. G. Creel, T. C. Chang, and R. C. Rudolph, Literary Chinese by the Inductive Method, 2 vols. (Chicago, 1938-1939).
《依靠归纳法的中国文士》
《穀梁传》 《十三经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南昌,1815)。
《公羊传》 《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南昌,1815)。
郭 郭沫若:《金文丛考》(东京,1932)。
郭(2)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东京,1935)。
郭(3) 郭沫若:《十批判书》(重庆,1945)。
《国语》 《国语》(四部丛刊本)。
H
哈龙 Gustav Haloun, "Fragmente des Fu-tsi und des Tsin-tsi. Fruhkonfuzianische Fragmente I," in Asia Major VIII (Leipzig, 1933), 437-509.
《前儒家著作残篇,卷一》
哈龙(2) Gustav Haloun, "Das Ti-tsi-tsi. Fruhkonfuzianische Fragmented II," in Asia Major, IX (Leipzig, 1933), 467-502.《前儒家著作残篇,卷二》
哈特斯利 Alan F, Hattersley, A Short History of democracy (Cambridge, 1930).
《民主简史》
哈德森 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London, 1931).
《欧洲与中国》
《韩非》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1896)。
《韩非》(2) 《韩非子全书》,W. K. 廖译,卷一(伦敦,1939)。
韩愈 《朱文公校韩昌黎先生集》(四库丛刊本)。
《汉书》 王先谦:《前汉书补注》(1900)。
《汉书》(2) 班固:《汉书》, Homer H. Dubs译,卷一和卷二(Baltimore, 1938and1944)。
赫恩肖 F. J. C. Hearnshaw, "Chivalry, European," in ESS III, 436-441.
《骑士,欧洲人》
赫梅尔 William F. Hummel, "K' ang Yu-wei, Historical Critic and Social Philosopher, 1858-1927," i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IV (Glendale, Calif., 1935), 343-355.
《康有为,历史批评家和社会哲学家》
胡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第15版(上海,1930)。
胡(2) 胡适:《王莽,十九个世纪前的社会主义皇帝》,载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LIX(上海,1928),218-230。
胡(3) 胡适:《作为汉代国教的儒学的创立》,载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LX (上海,1929),20-41。
胡(4) 胡适:《儒学》,载ESS,IV,198-201。
胡(5) 胡适:《胡适论学近著》卷一(上海,1935)。
胡(6) 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芝加哥,1934)。
《淮南子》 《淮南子》(四部丛刊本)。
黄 黄式三:《论语后案》(1844)。
霍夫丁 Harald Hoffding, A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 tr.by B. E. Meyer, Vol.II (1900;reprinted London, 1920).
《现代哲学史》
霍尔库姆 A. N. Holcombe, Government in a Planned Democracy (New York, 1935).
《有计划的民主政治》
霍尔库姆(2) A. N. Holcombe, "Chinese Problem," in ESS, III, 431-436.
《中国的难题》
J
吉本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3 vols. (1776-1788;reprinted New York, 1946).
《罗马帝国衰亡史》
《家语》 《孔子家语》(四部丛刊本)。
贾格尔 Fritz Jager, "Der heutige Stand der Schi-ki-for-schung,“ in Asia Major, IX (Leipzig, 1933), 21-37.
《〈史记〉研究之现状》
《杰出的中国人》 Arthur W. Hummel, de. 桓慕义,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 ing Period, 2 vols. (Washington, 1943-1944).
《清代杰出的中国人》
杰弗逊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ed. by Paul Leicester Ford, 10 vols. (New York and London, 1892-1899).
《杰弗逊文集》
杰弗逊(2) The Commonplace Book of Thomas Jefferson, ed.by Gilbert Chinard (Baltimore and Paris, 1926).
《杰弗逊札记》
杰弗逊(3) The Life and Selected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ed. by Adrienne Koch and William Peden (New York, 1944).
《杰弗逊生平和文选》
《经典释文》 陆德明:《经典释文》(四部丛刊本)。
K
卡伦 Horace M. Kallen, "Pragmatism," in ESS, XII, 307-311.
《实用主义》
卡尔卡松 E. Carcassone, "La Chine dans i' Esprit des Lois," in Revued' Histoire Litteraire de la France, 31 Annee (Paris, 1924), 193-205.
《中国的法律精神》
卡西里尔 Ernst Cassirer, "Kant, Immanuel," in ESS, VIII, 538-542.
《康德》
康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1897;北京重印,1922)。
康德 Immanuel Kant's Sammtliche Werke, ed.by K. Rosenkranz and F. W. Schubert, 14 vols (Leipzig, 1838-1842).
《康德全集》
康德(2) 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reprint of translation published in London in 1796, translator unnamed (Los Angeles, 1932).《永久和平》
科克 Adrienne Koch, The Philosophy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1943).
《杰弗逊的哲学》
克拉克 E. A. Kracke, Jr. , "Family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se, X (Cambridge, 1947), 103-123.
《帝制下的中国科举考试的得与失》
克里尔,洛兰 Lorraine Creel, The Concept of Social Order in Early Confucianism (unpublished Ph. D. de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43).
《早期儒学的社会秩序的思想》
肯尼迪 George A. Kennedy,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 ung-Ch' iu,"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LXII (Baltimore, 1922), 40-48.
《释〈春秋〉》
魁奈 Francois Quesnay, "Despotisme de la Chine," in Oeuvres Economiques et Philosophiques de F. Quesnay, ed. by Auguste Oncken (Frankfort and Paris, 1888), 563-660. First published serially in the Ephimerides du Citoyen (Paris, 1767); translated in Maverick 141-304.
《中国的专制主义》
L
拉奇 Donald F. Lach, Contributions of Chinato German Civilization, 1648-1740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41).
《中国对德国文明的贡献》
拉奇(2) Donald F. Lach, "Leibniz and China,"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I (New York, 1945), 436-455.
《莱布尼茨与中国》
拉斯基 Harold J. Laski, "Democracy," in ESS, V, 76-85.
《民主政治》
莱布尼兹 Gottfried Wilhelm, Freiherr von Leibniz, Novissina Sinica, 2nd ed. (Leipzig? 1699).
莱茵伯格 Paul M. A. Linebarger, Government in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1938).
《中华民国政治》
赖克韦恩 Adolf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25).
《中国与欧洲,十九世纪文化和艺术的联系》
兰 Paul Henry Lang, 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41).
《西方文明中的音乐》
朗松 Gustave Lanson, "Le Rôle de l' Experience dans la Formation de la Philosophie du XVIII Siècle en France," in La Revue du Mois, IX (Paris, 1910): I."La Transformation des Idées Morales et la Naissance des Morales Rationelles de 1680 à 1715," 5-28; II. "L' Éveil de la Conscience Sociale et les Premières Idées de Réformes Politiques," 409-429.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成长中的经验的作用》:一、《1680年到1715年道德观念的转变和道德理性的诞生》;二、《社会良知的觉醒和政治改革的原初思想》
老子 《老子》,亦称为《道德经》。
勒马斯特 Bobert J. La Master, "Music Therapy as a Tool for Treatment of Mental Patients in the Hospital," in Hospital Management, LXII. 6 (Chicago, 1946), 110-114, LXIII. 1 (1947), 110-114.
《作为治疗住院精神病人之工具的音乐》
李明 Louis Daniel Le Comet, Memoirs and Observations...Made in a Late Journey Through the Empire of China, tr. from the Paris ed (London, 1697).
《观察与实录……作于新近的横穿中华帝国的旅行》(原译名为《中国现势新志》)
勒费弗尔 Georges Lefebvre,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 by R. R. Palmer (Princeton, 1947).First published as Quatre-vingt-neuf (Paris, 1939).
《法国革命的来临》
雷丁 Max Radin, "Jus Gentium," in ESS, VIII, 502-504.
《国际法》
里克 W. E. H. Lecky,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Influence of the Spirit of Rationalism in Europe, 2vols (New York, 1866).《欧洲理性主义的兴起和影响》
理雅格 The Chinsese Classics, tr. by James Legge, vols. I-II, 2nd ed. rev (Oxford, 1893-1895), vols.III-V (London, 1865-1872).
《礼记》 理雅格译,《东方圣典》XXVII和XXVIII(1885; reprinted London, 1926)。
梁 梁启超:《荀卿及荀子》,载《古史辨》卷四,104-115。
林 林语堂:《礼:中国社会管理和组织的原则》,载《中国社会和政治科学评论》,卷二,第一期(北京,1917),106-118。
林(2) 林语堂:《孔子的智慧》(纽约,1943)。
林赛 A. D. Lndsay, The Modern Democratic State, Vol, I (New York and London, 1947).
《现代民主国家》
刘鄂 刘鄂:《铁云藏龟》,保定重印(1931)。
刘宝楠 刘宝楠、刘恭冕:《论语正义》(初版,1866),载《皇钦经籍续编》(江阴,1886-1888),1051-1074。
罗 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1912)。
罗(2) 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1931)。
罗(3) 罗振玉:《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1938)。
罗杰斯 A. K. Rogers, The Socratic Problem (New Haven, 1933).
《苏格拉底的难题》
罗博瑟姆 Arnold H. Rowbotham, Missionary and Mandarin, the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42).
《传教士与士大夫,中国宫廷中的耶稣会士》
罗博瑟姆(2) Arnold H. Rowbotham, "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 in Far Eastern Quarterly, IV (1945), 224-242.
《儒学对十七世纪欧洲的撞击》
论卫励 Arthur O. Lovejoy, "The Chinese Origin of a Romanticism," i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Baltimore, 1948), 99-135.
《浪漫主义的中国之源》
《论语》 理雅格、韦利和其他人的译本。
《论语》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南昌,1815)。
《论语释》 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1943)。
M
Makino Makino Kenjiro,《史记国字解》卷七(Waseda大学;东京,1919)。
马伯乐 Henri Maspero, La Chine Antique (Paris, 1927).
《古代中国》
马伯乐(2) Henri Maspero, "La Composition et la date du Tso tchouan," in 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I (Brussels, 1932), 137-215.
《〈左传〉成书年代》
马弗里奇 Lewis A.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San Antonio, 1946).
《中国,欧洲的楷模》
麦考利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The Romance of History. England. By Henry Neele." Unsigned review in The Edinburgh Review, XLVII (Edinburgh, 1828), 331-367.
《历史传奇,英格兰》
梅 梅思平:《春秋时代的孔子和孔子的政治思想》,载《古史辨》卷二,161-194。
梅里亚姆 Charles E. Merriam, The New Democracy and the New Despotism (New York and London, 1939).
《新民主与新专制》
《孟子》 《孟子》,理雅格译。
《孟子》 《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南昌,1815)。
孟德斯鸠 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s, tr. by Thomas Nugent, 2 vols (Cincinnati, 1873).
《法的精神》
《墨子》 孙诒让:《墨子间诂》(1895)。
《墨子》(2) 《墨子的伦理和政治著作》,梅贻宝译(伦敦,1929)。
莫利 John Viscount Morley, Diderot and the Encyclopaedists, Vol.I (London, 1923).
《狄德罗与百科全书派》
O
欧文 William A. Irwin, "The Hebrews," in Intellectual Adventure, 223-360.
《希伯来人》
P
珀切斯 Samuel Purchas, Hakluytus Posthumo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s, Vol.XII (1625;reprinted Galsgow, 1906).
《Hakluytus的遗作或珀切斯对他的膜拜》
皮克 Bernhard Pick, The Extra-Canonical Life of Christ (New York, 1903).
《基督的越轨生涯》
皮诺特 Virgile Pinot,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i' 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 (1640-1740) (Paris, 1932).
《法国哲学精神中的中国成分》
皮诺特(2) Virgile Pinot, "Les Physiocrates et la Chine au XVIII siecle," in Revue d' Histoire Modern et Contemporaine, VIII (Paris, 1906-1907), 200-214.
《十八世纪的中国重农主义者》
蒲鲁塔克 Plutarch's Lives, "the translation called Dryden's," rev. by A. H. Clough, Vol.II (Boston, 1864).
《蒲鲁塔克的生活》
普维里 Picrre Poivre, Travels of a Philisopher, tr. from French, translator unnamed (Dublin, 1770).
《一位哲学家的旅行》
Q
齐 齐思和:《战国制度考》,载《燕京学报》第24期(北京,1938),159-219。
齐(2) 齐思和:《商鞅变法考》,载《燕京学报》第33期(北平,1947),163-194。
钱玄同 钱玄同:《论诗经真相书》,载《古史辨》卷一,46-47。
钱穆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上海,1936)。
钱穆(2) 钱穆:《论语要略》(1915;上海重印,1934)。
《钦定春秋》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1721;江南书局重印,1888)。
钦纳德 Gilbert Chinard, Thomas Jefferson, the Apostle of Americanism, 2nd de., rev. (Boston, 1946).
《托马斯·杰弗逊,美国主义的倡导者》
钦纳德(2) Gilbert Chinard, "Jefferson and the Physiocrats," 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hronicle, XXXIII (Berkeley, 1931), 18-31.
《杰弗逊与重农主义》
R
容肇祖 容肇祖:《韩非子考证》(上海,1936)。
容庚 容庚:《金文编》(长沙,1939)。
S
《商君书》 《商君书》,戴闻达译(伦敦,1928)。
《诗》 《中国古典》,理雅格译,卷四(伦敦,1871)。
《诗》(2) 《歌本》,韦利译(波士顿和纽约,1937)。
《诗注疏》 《十三经注疏·毛诗注疏》(南昌,1815)。
《史记》 Takigawa Kametaro,《史记会注考证》,十卷本(东京,1932-1934)。
《史记》(2) 司马迁《史记》,沙畹译,五卷本(巴黎,1895-1905)。
施莱奥克 John K. Shryock,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Cult of Confucius (New York and London, 1932).
《对孔子的国家崇拜的起源和发展》
《书》 《中国古典》,理雅格译,卷三(伦敦,1865)。
孙海波 孙海波:《甲骨文编》(北平,1934)。
孙逸仙 孙中山:《中山丛书》,第三版,四卷本(上海,1927)。
孙逸仙(2) 孙逸仙:《三民主义原理》,Frank W. Price译(上海,1929)。
孙逸仙(3) 孙逸仙:《孙中山的三权分立制》,paschal W. D' Elia译(武昌,1931)。
T
《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扬州,1806)。
泰勒 A. E. Taylror, Socrates (1932; reprinted Edinburgh, 1933).
《苏格拉底》
汤 汤用彤:《王弼〈易经〉、〈论语〉新注》, Walter Liebenthal译,载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X (Cambridge, 1947), 124-161。
特里高尔特 Nicholas Trigault, The China That Was, tr. by L. J. Gallagher, from work published in 1615 (Milwaukee, 1942).
《这就是中国》
W
韦利 Waley译《论语》(1938;伦敦重印,1945)。
韦利(2) Arthur Waley, "The Book of Changes," in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 (Stockholm, 1933), 121-142.
《变化之书(易经)》
韦利(3) Arthur Waley, The Way and Its Power (London, 1934).
《大道及其力量》
韦伯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d ed.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1946).《社会学论文集》
韦勒斯 G. Weulersse, "The Physiocrats," in ESSV, 348-351.
《重农主义》
韦慕廷 C. Martin Wilbur, 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 (Chicago, 1943).
《西汉时期的奴隶》
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 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 tr. by G. H. and A. P. Danton (London, 1931).
《孔子与儒学》
威廉姆逊 H. R. Williamson, Wang An Shih, 2vols (London, 1935-1937).
《王安石》
威尔逊 Hohm A. Wilson, "Egypt," in Intellectual Adventure, 31-121.
《埃及》
威特福格尔 Karl August Wittfogel, "Public Office in the Liao and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X (Cambridge, 1947), 13-40.
《辽代的官职与科举制度》
《伪书》 江心诚编:《伪书通考》(长沙,1939)。
《文化探险》 H. and H. A. Frankfort, John A. Wilson, Thorkild Jacobsen, William A. Irwin, The Intellectual Adventure of Ancient Man (Chicago, 1946).
《古人的文化探险》
温德尔班克 Wilhelm Windelband,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tr. by James H. Tufts (New York, 1923).
《哲学史》
吴 吴大成:《愙斋集古录》(1896)。
X
西塞罗 Cicero, The Speeches, tr. by M. H. Watts (London and New York, 1923).
《讲演录》
修中诚 E. R. Hughes,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Mean-in-action (New York, 1943).
《大学与中庸》
许 许仕廉:《孙逸仙及其政治和社会思想》(洛杉矶,1933)。
《荀子》 梁启雄:《荀子柬释》(上海,1936)。
《荀子》(2) 《荀子的著作》,德效骞译(伦敦,1928)。
《荀子》(3) 王先谦:《荀子集解》(1891)。
Y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s Politics, tr. by Benjamin Jowett (1905; reprinted Oxford, 1931) (Pagination given as in Bekker).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雅各布森 Thorkild Jacobsen, "Mesopotamia," in Intellectual Adventure, 125-219.
《美索不达米亚》
叶 叶蠖生:《殷虚书契前编集释》(上海,1934)。
阎若璩 阎若璩:《校正四书释地》(1803)。
《盐铁论》 桓宽:《盐铁论》(四部丛刊本)。
《盐铁论》(2) Esson M. Gale译(Leyden,1931)。
《晏子》 《晏子春秋》(四部丛刊本)。
《易经》 理雅格译,载《东方经典》XVI,第二版(牛津,1899)。
《仪礼》 John Steele译,两卷本(伦敦,1917)。
Z
《战国策》 《战国策》(四部丛刊本)。
张国淦 张国淦:《汉石经碑图》(北平,1931)。
张荫麟 张荫麟:《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载《清华学报》卷一(北京,1924),38-69。
朱 朱谦之:《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长沙,1940)。
《庄子》 理雅格译,《东方经典》XXXIX,125-392 and XL,1-232(1891;伦敦重印,1927)。
《左传》 《中国古典》,理雅格译,五卷本(伦敦,1872)。
《左传注疏》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注疏》(南昌,1815)。
索引
译后记
士与中国文化
- 本书简介
- 新版序
- 引言——士在中国文化中上的地位
- 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
- 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
- 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兼论“俳优”与“修身”
- 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
- 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
- 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 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
-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 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概论——《朱子文集》序
- 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
- 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
- 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本书简介
作者:余英时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从本书内容可以明显看出余英时的见识远不如其师钱宾四先生:
初版“自序”是从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 的观点凸显“士”的中国特色。十五年后重读一次,我的基本看法仍然没有改变。当时我曾指出,“士”的“明道救世”精神在西方只能求之于中古基督教的传统。后来我读了意大利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 的《狱中笔记》,他将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现代知识人比之于中古的教士(priest) ,恰好印证了我的观察。(见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 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9, p.331) 所以我仍将这篇“自序”保留在新版中。
还有下面这段话:
但是我们知道,西方学人几乎一致认定,上述那种具有特殊含义的“知识分子”是近代的产物。“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言,其出现的时代大概不能早于18世纪。社会学家曼罕曾说,近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固定的经济阶级,知识和思想则成为他们唯一的凭借,因此他们才能坚持自己的“思想上的信念”。这个说法又几乎和孟子关于“士”的观察不谋而合:“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我们忍不住要追问:为什么知识分子阶层在西方出现得这样迟,而中国竟早在先秦时代便已产生了“士”呢?中国的“士”自孔子以来便形成了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西方近代知识分子难道竟没有历史的渊源吗?
为什么?承认中国比远西诸国早两千年进入“现代社会”就那么难吗?西方知识分子难道不是在明末以来的“中国热”的影响下才产生的吗?(乐~
本书最佳的部分就是关于汉代循吏、士商合流的研究。
新版序
《士与中国文化》初版刊行于一九八七年。十五年来我在同一园地中又继续做了一些垦荒的尝试,现在趁着再版的机会,选进了论旨最相近的论文四篇,以扩大新版的面貌呈现于读者的眼前。以下让我先对新版的内容稍作说明,然后再提出一两点通贯性的历史观察,以为读者理解之一助。
第一至第八篇基本上没有更动,只有第八篇增添一个附录——《士魂商才》,稍有补充。但初版时我未能亲校一遍,误字、遗漏、错简等等触目多有,使我一直对读者怀着愧仄。这次细读校样,作了一次相当彻底的改正。费时最多的是所引史料原文的校订;凡是可疑之点,我都重检原书,一一还其本来面目。初版“自序”是从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 的观点凸显“士”的中国特色。十五年后重读一次,我的基本看法仍然没有改变。当时我曾指出,“士”的“明道救世”精神在西方只能求之于中古基督教的传统。后来我读了意大利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 的《狱中笔记》,他将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现代知识人比之于中古的教士(priest) ,恰好印证了我的观察。(见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 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9, p.331) 所以我仍将这篇“自序”保留在新版中。
第九至第十二篇都是一九八七年以后所写。第九篇是最新研究所得的一个初步报告。自一九九九年以来,我以朱熹为出发点,详细研究了两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全书刚刚脱稿,与本书篇幅相等,不久即将印行。读者阅过本书所收《概论》之后,如果还想进一步了解“士”与宋代文化的关系,可以参考《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第十篇《士商互动》可以说是第八篇的一个续篇,更深入地探索了明、清商人的精神世界和“士”在其中的活动与作用。第十一篇论曾国藩的“士大夫之学”是个案研究,具体地显示出一个在朝的“士大夫”对于文化修养的关怀。但这篇个案如果和“士大夫”的传统联系起来,也折射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值得注目的侧影。汉代的循吏便早已重视“教化”,往往在朝廷所规定的“吏职”之外,主动地承担起儒家的“师”的责任。所以他们所至“讲经”并建立学校。宋、明儒学复兴,此风更为普遍,书院的历史便是明证。即以曾国藩的时代而论,在他之前有毕沅和阮元,在他之后还有晚清的张之洞。我藉曾国藩为例,抉出“士”的这一中国特征,并将“士”的历史研究推展至中西文化开始正面接触的时代。最后一篇《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属于通论性质,无论是风格或文体都与其他各篇颇有不同。这需要略作解释。这篇文字是应日本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佐藤慎一教授之约,为《中国——社会と文化》学报特别撰写的。此文最先刊布在该学报第五号中(一九九〇年六月) 。为了便于日译者的理解,我在选择重点和行文方面都特别力求清楚和浅显。“知识人”这个名词也是借用“intellectual”的日译。现在收入本书,一切仍依汉文原稿,不作更改。但是近十二年后的今天,我反而觉得“知识人”比“知识分子”更为适切。大约是一两年前,我曾读到一篇谈“分子”的文章,可惜已忘了作者和出处。据作者的精到分析,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近来极力避免“知识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识人”。我想尽量恢复“intellectual”的“人”的尊严,对于中国古代的“士”更应如此。把孔、孟、老、庄一概称之为“知识分子”似乎总不免感觉着有点别扭。但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我只能求一己的心安,却不敢奢望别人也同情我的感觉取向。
本书所集结的论文大体上都属于专题研究的性质,不过论旨有广狭之异、涵盖的时间也有长短之别而已。在每一专题的研究过程中,我都试图通过多方面的分析,以凸显“士”在某一历史阶段所表现的特殊风貌。我当然承认,整体地看,“士”在中国史上确然形成了一个具有髙度连续性的传统。但是专业史学更要求我去抉发“士”因时代不同而不断变动的轨迹。这样我便不能不在整体连续之中,特别注意个别时代之间“士”的传统所呈现的变异或断裂的一面。本书上起春秋,下迄清代,长达两千多年。“士”在每一时期的变异也就是中国史进人一个新阶段的折射。无论是从思想基调或活动方式看,“士”在这两千多年中都是迁流不居的。下面让我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说明我的论点。
清代沈垚(一七九八~一八四〇) 曾指出:“宋、元、明以来变迁之较”是“天下之士多出于商。”这确是一个有眼光的历史观察,所以受到现代史学家的重视。他是从科举制度的社会背景方面为“士”的古今之变划分阶段的。另一方面,从思想史的角度说,现代学者也将“宋明理学”划人同一阶段。这样一来,似乎社会史和思想史互相支援,宋代和明代的“士”应该是一脉相承,属于同一类型了。但是深一层分析,我们便发现,这两个不同朝代下的“士风”竟截然相异。同是理学家,朱熹和陆九渊都一心一意向往着王安石的“得君行道”,在皇帝面前也侃侃而谈,俨然以政治主体自居,充分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朱熹在他许多长篇大论的《封事》和《奏札》中,反复要求皇帝除旧布新,重建一个合理的秩序。对照之下,王守仁除了正德元年(一五〇六) 《乞宥言官去权奸》一疏,因而放逐龙场之外,其余奏疏多关具体事务,极少涉及朝政。正德十五年他写了一篇《谏迎佛疏》,期待皇帝效法“尧、舜之圣”,恢复“三代之圣”。这显然是承继了宋代“士”的精神,与王安石、朱熹等人的思路是一致的。但是这篇疏文却是“稿具未上”。(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卷九,页二九三——二九六) 更可注意的是同年他第一次和王艮会面,后者迫不及待地要谈怎样致君于尧、舜的问题,他立刻以“思不出其位”为理由,阻止了政治讨论。(见《王心斋先生全集》卷一《年谱》正德十五年条) 王艮后来写《明哲保身论》,讲学也转重“百姓日用之道”,断然与这次会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一对照,我们才清楚认到,宋代从王安石、二程到朱熹、陆九渊等人所念兹在兹的“得君行道”,在明代王守仁及其门人那里,竟消失不见了。这个“变异”或“断裂”还不够使人惊异吗?然而问题还远不止此。
十六世纪以后,部分地由于阳明学(或王学) 的影响,仍然有不少的“士”关怀着合理秩序的重建,但是他们的实践方向已从朝廷转移到社会。东林讲友之一陈龙正所标举的“上士贞其身,移风易俗”(《明儒学案》卷六十) 可以代表他们集体活动的主要趋向。所以创建书院、民间传教、宗族组织的强化、乡约的发展,以至戏曲小说的兴起等等都是这—大趋向的具体成果。其中有些活动虽在宋代已经开始,但一直要到十六世纪以后才获得充分的展开。用现代的话说,明代的“士”在幵拓社会和文化空间这一方面显露出他们的特有精神。这当然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密切的关系。第一是政治的环境。宋代承五代武人跋扈之后,重文轻武,以争取“士”阶层的支持,因此采取了对“士”特别优容的政策。陈寅恪所谓“六朝及天水(赵宋) 一代思想最为自由,”便指此而言。(见《论再生缘》,收在《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二〇〇一年,页七二) 明代则继蒙古统治而起,“士”已落到“九儒、十丐”的地位。而朱元璋又遇“士”至酷,以至有士人“断指不仕”的情况。(见《明史》卷九四《刑法二》,中华本,页二三一八) 宋代“士”的政治主体意识自然不可能继续发挥,“得君行道”更是无从谈起。第二是社会的变迁。十六世纪以后市场经济的新发展和商人地位的上升是“士”的转向的另一重要背景。明代的“士”恰好在同一时期展开了开拓社会和文化空间的活动决不是偶然的。商人的财富为这些活动提供了经济基础。除本书第八、第十两篇已有详细讨论之外,我又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见《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中续加论证。这里便不必多说了。宋、明两代的“士”不容混为一谈,这是十分明显的历史事实。不但他们的活动取向不同,思想也有极大的分歧。所谓“宋明理学”,如果从政治、社会以至经济的角度作深人的解读,其中断裂之点也不是表面的连续所能掩盖的。
在本书初版《自序》中,我比较着重地指出:“士”在中国史上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这当然是强调连续性的一面。原序虽然也同时指出,“士”的传统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风貌,而不是静止不变的,但毕竟没有作迸一步的解释。为了避免引起可能的误解,我在上面特别举例说明这一传统的断裂状态。我为什么以宋、明两代的对比为例呢?这是因为把十六世纪划为新阶段的开始是我从最近研究中所得到的一个初步看法,而这个看法则又在《朱熹的历史世界》的撰写过程中,获致进一步的加强。我决不敢自以为是。我的看法最后很可能为未来的史学研究所否证,但目前则不妨提出来,作为一个待证的假设。
这里引出了一个很重要问题:“传统”一词本身便涵蕴着连续不断的意思。然则所谓“断裂”,相对于“士”的传统而言,究竟居于何种地位呢?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这里所谓“断裂”都是指“传统”内部的“断裂”,因此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事实上,每经过一次“断裂”,“士”的传统也随之推陈出新一次,进人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而连续性则贯穿在它的不断的内部“断裂”之中。西方学者曾将基督教的“传统”形容作“永远地古老,永远地新颖”(“ever ancient, ever new”,见Jaroslav Pelikan, The Vindication of Traditi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8) 。这句话的意思和古语“与古为新”很相近,也可以一字不易,移用于“士”的传统。
“士”的传统既是一活物,在一个接一个的内部“断裂”中更新自身,那么它最后为什么走向解体,从历史上隐没了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此处自不能轻率作答;但因与本书的论旨有关,我也不能不略陈所见,以结束这篇序文。让我先借一个著名的古典簪喻为讨论的始点。杜牧《注孙子序》论“盘之走丸”说:
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樊川文集》卷十)
“士”的传统可比之于“盘”,而“士”在各阶段的活动,特别是那些“断裂”性的发展,则可比之于“丸”。过去两千多年中国之所以存在着一个源远流长的“士”的传统,正是因为“士”的种种思想与活动,尽管“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并没有越出“传统”的大范围,便像丸未出盘一样。而这一传统之所以终于走进历史则是因丸已出盘,原有的传统架构已不足以统摄“士”的新“断裂”活动了。
最迟从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已逐渐取得一个共识士”(或“士大夫”) 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知识人(即“intellectual”,通译为“知识分子”) ,知识人代士而起宣告了“士”的传统的结束;这便是本书研究的下限。这个下限的断代应该划在何时呢?大致上说,十九与二十世纪交替之际是关键的时刻。如果要进一步寻找一个更精确的日期,我以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 科举废止是一个最有象征意义的年份。这一点和“士”的性质有关,不能不略作解释。“士志于道”——这是孔子最早为“士”所立下的规定。用现代的话说,“道”相当于一套价值系统。但这套价值系统是必须通过社会实践以求其实现的;唯有如此,“天下无道”才有可能变为“天下有道”所以“士”在中国史初出现的时候便有了参与“治天下”的要求。这个要求是普遍的,并不仅限于儒家。司马谈告诉我们:“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刘向论名家也“论坚白异同,以为可以治天下”。这更证实了司马谈的说法。(见本书第一篇) 先秦以来“士”的参政要求,由于种种因缘,竟在汉代实现了。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独尊儒术”的提议之后,不但郡县举孝廉改以“士”为对象,太学中博士弟子更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从此汉代郎、吏由“士”出身便制度化了。博士弟子“甲科”为郎已是考试的结果;东汉顺帝阳嘉元年(一三二) 不但规定孝廉限于“诸生”和“文吏”两项,而且还要加以考试。(详见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收在《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一九九一年;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部分) 这便是科举制度的滥觞。“士大夫”作为一广泛的社会称号始于两汉之际(见本书第五篇) ,恰好与科举(广义的) 制度的成立相先后,这决不是偶然的。所以从社会结构与功能方面看,从汉到清两千年间,“士”在文化与政治方面所占据的中心位置是和科举制度分不开的。通过科举考试(特别如唐、宋以下的“进士”) ,“士”直接进入了权力世界的大门,他们的仕宦前程已取得了制度的保障。这是现代学校的毕业生所望尘莫及的。着眼于此,我们才能抓住传统的“士”与现代知识人之间的一个关键性的区别。清末废止科举的重大象征意义在此便完全显露出来了。但是我必须补充一句,以现代学校取代科举考试,仍然出于清末士大夫的主张和推动。(参看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第六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这是“士”的传统的最后一次“断裂”;但这次“断裂”超过了传统架构所能承受的限度,“丸”已出“盘”,“士”终于变成了现代知识人。
但是“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五四”时代知识人追求“民主”与“科学”,若从行为模式上作深人的观察,仍不脱“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流风余韵。一位西方思想家在二十世纪末曾对中国知识人的这种精神感到惊异。他指出中国知识人把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看成他们的独有的责任,这是和美国大相径庭的。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这些价值的追求是大家的事,知识人并不比别人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他因此推断,这一定和中国儒家士大夫的传统有关。(见Michael Walzer, Thick and Thin, Moral Argument at Home and Abroa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4, pp.59~61) 他完全猜对了。现代知识人不在本书研究的范围之内,这里不必多说。我引这一段“旁观者清”的话,只是为了说明,本书所探讨的对象虽是历史陈迹,它所投射的意义却可能是现代的。
余英时
二〇〇二年九月廿二日
于普林斯顿
引言——士在中国文化中上的地位
这部《士与中国文化》集结了八篇历史研究的专论,其主要的对象都是“士”。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为了尊重历史事实,这里依然沿用了“士”的旧称。这几篇研究文章基本上采取了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因此全书定名为《士与中国文化》。
士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决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但是无可争辩的是,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本书所企图观察和呈现的是: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不用说,这当然只能是一种宏观的历史。但宏观若不能建筑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则将不免流于空泛和武断。因此本书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我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我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中国文化自成一独特的系统,这已是今天中外大多数学人所共同承认的历史事实。在西方文化的对照之下,这一文化系统的独特性更是无所遁形。但是文化的范围几乎是至大无外的,我们很难用几句简单扼要的话把中国文化的特性刻画得恰如其分。近几十年来,讨论中西文化异同的文字多至不可胜数,真是陷入了墨子所谓“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纷乱状态。不过如果越过语言的层次,我们便不难发现各家的说法在表面上虽然分歧很大,实际上却未必互不相容。与西方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几乎在每一方面都表现出它的独特形态。因此观察者从任何角度着眼,都可以捕捉到这种独特形态的一个面相。这是众说纷纭的根本起因。只要观察者不坚持以偏概全,则观点愈多,愈能彰显中国文化的特性。本书定名也部分地取义于此:通过“士”这一阶层的历史发展来探索中国文化的独特形态。
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含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含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也愈显出它的力量。所以汉末党锢领袖如李膺,史言其“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又如陈蕃、范滂则皆“有澄清天下之志”。北宋承五代之浇漓,范仲淹起而提倡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终于激动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和豪情。晚明东林人物的“事事关心”一直到最近还能振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弦。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
但是我们知道,西方学人几乎一致认定,上述那种具有特殊含义的“知识分子”是近代的产物。“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言,其出现的时代大概不能早于18世纪。社会学家曼罕曾说,近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固定的经济阶级,知识和思想则成为他们唯一的凭借,因此他们才能坚持自己的“思想上的信念”。这个说法又几乎和孟子关于“士”的观察不谋而合:“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我们忍不住要追问:为什么知识分子阶层在西方出现得这样迟,而中国竟早在先秦时代便已产生了“士”呢?中国的“士”自孔子以来便形成了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西方近代知识分子难道竟没有历史的渊源吗?
这些带有根本性质的大问题是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的。但是上述两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中国有一个两千多年的“士”的传统,而西方“知识分子”出现于近代——则值得我们认真地思索。必须说明,虽然中国的“士”和西方的“知识分子”在基本精神上确有契合之处,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两者之间可以画等号。我们固然可以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发现“士”的明显遗迹,然而他毕竟不是传统的“士”了。“士”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歧异不是这篇短序所能涉及的,我在下面只想说明一点:中国史上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士”阶层似乎更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性,也似乎更能说明中西文化的异质之所在。
从思想史的观点看,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的起源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关系最为密切。康德曾给启蒙运动的精神下了一个简明扼要的界说,即“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这句话恰好可以代表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但这一精神的出现却必须从西方文化的全部背景中去求了解。“理性”源于古代希腊,代表了西方文化的最原始并且也是最主要的特征。古希腊理性的最重要的结晶则无疑是哲学(包括科学在内)。所以古希腊的哲学家可以说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原型,但是古代哲学家在精神上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颇有不同。古希腊的“理性” 主要表现为“理论的理性”或“思辨的理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世界一分为二:一方面是超越的本体或真理世界,另一方面是现实的世界。这是“外在超越”型文化的特色。两个世界的清楚划分是西方文化的特显精彩之处,然而也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之一即是二分的思维方式的普遍流行。二分思维虽非西方所独有,但确是西方文化中一个极为强烈的倾向,理论和实践的二分便是其具体的表现之一。“理论的理性”只对永恒不变的真理世界感兴趣,扰攘的现实世界是不值得注意的,因为前者是“本体”,后者不过是“现象”而已。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家的全副生命都应该奉献于对永恒事物的探究;现象界尽管千变万化,而哲学家所追求的则只是万象纷纭后面的不变原则。西方文化史上一向有“静观的人生”(vita contemplativa)和“行动的人生”(vita activa)的二分,其源即在古代希腊。拉丁文所谓“静观”便是从希腊文所谓“理论”(theōria)翻译出来的,这是西方“理论”一词的古义。古希腊哲学家所向往的是“静观的人生”而不是“行动的人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以“静观冥想”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有人更指出,柏拉图的《共和国》是城邦社会的理想化,其最主要的目标便是为哲学家提供一个“静观冥想”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可以不受一切世俗活动(包括政治活动)的干扰。无可否认的,古希腊的哲学家确是以“精神贵族”自居,他们虽然重视“理性”,但是他们的“理论的理性”是不屑于用之于康德所谓“公共事务”上面的。所以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和古希腊哲学家之间并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前者所关注的不是“静观的人生” ,而是“行动的人生”;不是“理论”,而是“实践”。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在《论费尔巴哈纲领》第十一条的名言:“哲学家从来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真正的关键是改变它。”这句话最能表示一个近代“知识分子”和古希腊以来的传统哲学家之间的分歧所在。“解释世界”是“静观”的结果;“改变世界”才代表近代“知识分子”重“行动”或“实践”的精神。所以在《纲领》第一条中,马克思开宗明义便指出:一切现存唯物哲学的主要缺点在于持“静观的”方式看待真实的事物。费尔巴哈也仍然在古代哲学家的精神的笼盖之下,故重视理论而轻忽实践,其基本态度是“静观的”而不是“行动的”。
但是康德所说的启蒙精神中的道德勇气则又和基督教的传统有渊源。西方的基督教是希伯来的“信仰”压倒了古希腊的“理性”以后的产物,因此在整个中古时代哲学变成了神学的“婢女”。古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宗教之间虽有冲突和紧张,然而两者确有一相合之点,即同属于“外在超越”的形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已从哲学内部推断宇宙间必有一个超越的“不动的动力”;罗马斯多葛派的哲学家更发展出一个非常接近人格神的上帝观念。所以一般文化史家颇相信古代后期的哲学已在思想上为西方人接受希伯来的宗教作好了准备工作。罗马的国家组织和普遍性的法律又恰好为这种外在超越的宗教提供了形式化的榜样,于是中古基督教的普遍教会组织便顺理成章地形成了。由于基督教实际上垄断了中古欧洲的精神世界,我们如果想在这个时期寻找一个相当于近代“知识分子”的阶层便唯有向基督教求之。基督教是一种“救世”的宗教,它不但为西方文化树立了最高的道德标准,而且持此标准以转化世界。从积极的一方面看,它在中古文化史上的贡献是无可否认的。基督教的教士之中,有人教化了入侵的蛮族,有人驯服了君主的专暴权力,更有人发展了学术和教育。显然和古希腊的哲学家不同,他们做的正是改变世界的工作。古希腊哲学家并没有对奴隶制度提出怀疑,中古教士则明白地宣称奴隶制度是不道德的,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就文化和社会的使命感而言,欧洲中古的教士确具有近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之一面。但是另一方面,基督教又有严重的反知识、轻理性的倾向;知识必须从属于信仰,理性也必须匍匐于上帝的“启示”之下。这便和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背道而驰了。
从上面的简略回顾,我们清楚地看到: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虽与古希腊的哲学家和基督教的教士在精神上、思想上都有很深的渊源,但三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西方学人之所以视“知识分子”为近代文化的产品,而不强调其古代和中古的远源,其故端在于是。一部西方近代文化史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俗世化”(secularization)的过程。这一过程至18世纪的启蒙时代才大致初步完成,因为启蒙思想家真正突破了教会的权威,而成为俗世“知识分子”的先行者。在此之前,承担着西方“社会的良心”的仍然是基督教,特别是宗教改革以来的新教各派,如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即使在今天,西方宗教人士也还在继续关怀人类的命运,所谓“解放神学”或“革命神学”的出现即足以说明当代的基督教仍然坚持其“改变世界”的传统。而另一方面,古希腊哲学家“静观冥想”以追求永恒真理的精神也有其近代的承继者,即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家。西方现代学院派的哲学家,特别是代表主流的分析哲学家,更可以说是直接继承了古希腊的传统。
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知识分子”则显然代表一种崭新的现代精神。和基督教的传统不同,他们的理想世界在人间不在天上;和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也不同,他们所关怀的不但是如何“解释世界”,而且更是如何“改变世界”。从伏尔泰到马克思都是这一现代精神的体现。
在西方的传统对照之下,中国“士”的文化特色是极为显著的。如果我们断言孔子揭开了中国传统思想史的序幕,那么在启幕之际中国思想便已走上与西方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国当然也发生了超越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分化,但是这两个世界却不是完全隔绝的;超越世界的“道”和现实世界的“人伦日用”之间是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西方人的二分思维方式在中国思想史上自始即不占重要地位。中国思想家所强调的则是“即知即行”、“即动即静”那种辩证式的思维,故往往在“相反”中看见“相成”。换句话说,中国的超越世界没有走上西方型的外在化之路。因此我们既看不到古希腊哲学中本体和现象两个世界的清楚划分,也看不到希伯来宗教中天国和人间的对峙。中国的“士”的历史是和传统思想史同时揭幕的。在这一特殊思想背景之下,“士”一方面与古希腊哲学家和基督教教士都截然异趣,而另一方面又有与两者相同之处。就“士”之重视“知识”而言,它是近于古希腊哲学家的;古人以“通古今,决然否”六个字表示“士”的特性,正可见“士”的最重要的凭借也是“理性”。但就“士”之“仁以为己任”及“明道救世”的使命感而言,它又兼备了一种近于基督教的宗教情操。近代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有把孔子比之于苏格拉底者,也有把孔子比之于耶稣者,这两种不同的比况都有理由,但也都不尽恰当。孔子来自中国文化的独特传统,代表“士”的原型。他有重“理性”的一面,但并非“静观冥想”的哲学家;他也负有宗教性的使命感,但又与承“上帝”旨意以救世的教主不同。就其兼具两重性格而言,中国的“士”毋宁更近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但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虽然在思想上与古希腊哲学和中古基督教都有渊源,其最直接的根据则是“俗世化”的历史发展。中国“士”的传统自先秦以下大体上没有中断,虽则其间屡有转折。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仍与基督教在西方中古文化中所取得的绝对的主宰地位有别。六朝隋唐之世,中国诚然进入了宗教气氛极为浓厚的时代,然而入世教(儒)与出世教(释)之间仍然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道教也处于出世与入世之间。故中国中古文化是三教并立,而非一教独霸。由于中国文化没有经过一个彻底的宗教化的历史阶段,如基督教之在中古的西方,因此中国史上也没有出现过一个明显的“俗世化”的运动。宋以后的新儒家可以说代表了“士”在中国史上的最后阶段,他们“出入老释”而复“返之六经”,是从宗教中翻身过来的人。但是他们仍然是直承先秦“士”的传统而来,其历史的线索是很清楚的。这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在传承上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谱系,适成有趣的对照。
中国“士”的传统的源远流长,如上文所已指出的,基本上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性。通过这一历史事实,我们可以更具体地辨清中西文化在起源和流变两方面的根本分歧之所在。必须说明,我们强调的仅仅是双方在文化形态上所表现的客观差异,而不在平衡两者的优劣。西方的“知识分子”出现在近代自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而尤其和基督教在中古定于一尊有密切的关系。从积极的方面看,中古西方的价值系统已统一在基督教之下。基督教现已完全承担了“社会良心”的任务,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在中古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存在的空间。即使是出现在中古末期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学者”也仍然不能称之为“世俗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价值系统方面并没有叛离基督教。中国史上则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基督教那种有组织的统一教会:所谓儒教根本没有组织,佛教和道教也没有统一性的教会。而且以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而言,儒教始终居于主体的地位,佛、道两教在“济世”方面则退处其次。这正是传统中国的“社会良心”为什么必然要落在“士”阶层身上的背景。
“士”的传统虽然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但这一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地,“士”是随着中国史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的。概略地说,“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但是在秦汉以来的两千年中,“士”又可更进一步划成好几个阶段,与每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密相呼应。秦汉时代,“士”的活动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以儒教为中心的“吏”与“师”两个方面。魏晋南北朝时代儒教中衰,“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道家“名士”(如嵇康、阮籍等人)以及心存“济俗”的佛教“高僧”(如道安、慧远等人)反而更能体现“士”的精神。这一时代的“高僧”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此时的中国是处于孔子救不得、唯佛陀救得的局面,“教化”的大任已从儒家转入释氏的手中了。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徒(特别是禅宗)继续其拯救众生的宏愿外,诗人文士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之伦更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宋代儒家复兴,范仲淹所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成为此后“士”的新标准。这一新风范不仅是原始儒教的复苏,而且也涵摄了佛教的积极精神,北宋云门宗的一位禅师说:“一切圣贤,出生入死,成就无边众生行。愿不满,不名满足。”一直到近代的梁启超,我们还能在他的“世界有穷愿无尽”的诗句中感到这一精神的跃动。
本书所收各文,依时代先后编排,大体上反映了“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特殊面貌。本书所刻画的“士”的性格是偏重在理想典型的一面。也许中国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完全符合“士”的理想典型,但是这一理想典型的存在终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它曾对中国文化传统中无数真实的“士”发生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鞭策作用。通过他们的“心向往之”,它确曾以不同的程度实现于各个历史阶段中。本书的目的仅在于力求如实地揭示“士”的理想典型在中国史上的具体表现,决不含丝毫美化“士”的历史形象的用意。我们虽然承认“士”作为“社会的良心”,不但理论上必须而且实际上可能超越个人的或集体的私利之上,但这并不是说“士”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人”可以清高到完全没有社会属性的程度。所谓“士”的“超越性”既不是绝对的,也决不是永恒的。从中国历史上看,有些“士”少壮放荡不羁,而暮年大节凛然;有的是早期慷慨,而晚节颓唐;更多的则是生平无奇节可记,但在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时刻,良知呈露,每发为不平之鸣。至于终身“仁以为己任”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士”,在历史上原是难得一见的。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则是现代一般观念中对于“士”所持的一种社会属性决定论。今天中外学人往往视“士”或“士大夫”为学者—地主—官僚的三位一体。这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偏见,以决定论来抹杀“士”的超越性。按之往史,未见其合。事实上,如果“士”或“知识分子”完全不能超越他的社会属性,那么,不但中国史上不应出现那许多“为民请命”的“士大夫”,近代西方也不可能产生为无产阶级代言的马克思了。
本书所持的基本观点是把“士”看作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相对的“未定项”。所谓“未定项”即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为社会属性所完全决定而绝对不能超越者。所以“士”可以是“官僚”,然而,他的功能有时则不尽限于“官僚”。例如汉代的循吏在“奉行三尺法”时固然是“吏”,而在推行“教化”时却已成为承担着文化任务的“师”了。“士”也可以为某一社会阶层的利益发言,但他的发言的立场有时则可以超越于该社会阶层之外。例如王阳明虽倡“士商异业而同道”之说,但他的社会属性显然不是商人阶级的成员。相对的“未定项”也就是相对的“自由”。从现代的观点言,这点“自由”似乎微不足道,然而从历史上观察,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一再地超越自我的限制,则正是凭借着此一“未定项”。研究“士”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不能不首先着眼于此的。
1987年6月21日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
知识阶层的兴起是中国古代社会演进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在追溯这一段历史发展的过程之前,我们必须先对“知识阶层”这个观念加以检讨。
“知识阶层”是西方近代的名词,它最初源于俄国的所谓“intelligentsia”。至于现在英文中的“intellectual”这个词,则起源甚迟,据学者考证,它大概是由法国“老虎总理”克里孟梭(G.Clemenceau) 在1898年首次使用的(intellectuel) 。另一方面,俄国的“intelligentsia”也是一个相当新的观念,它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中。 不过俄国“知识阶层”的远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贵族阶级。
由于“知识阶层”的观念起源很晚,以往一般的社会学家和史学家颇倾向于把这个社会阶层认作一个近代的现象。他们当然并不否认,在近代以前的每一历史阶段中都存在着一个“知识阶层”(intellectual stratum) 。但是,据他们的分析,这种生活在近代以前的静态社会中的知识阶层,其功能与近代的动态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截然不同。前者如古代印度的婆罗门或欧洲中古的僧侣,乃是垄断当时教化权力的特殊阶级,其主要的功能是在为当时流行的世界观提供理论的根据,为当时的政治、社会秩序作辩护士。因此,这一阶层在思想上是和日常的生活现实脱节的,他们的主要兴趣是为自己的武断思想作系统化的努力。欧洲中古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 便是这个阶层思想的典型代表。
与此相反,近代的自由知识分子既不复具有垄断教化的权力,因而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近代的知识分子来自各种不同的社会阶级,他们已没有一个组织严密的中古教会作后台了。为了争取社会上各种不同的集团的支持,他们现在只有在学术思想的领域内从事于公平而自由的竞争。
近代的知识阶层与中古以及古代的知识阶层,在性格上有显著的不同,这是无可置疑的。但上面所刻画的古今对比则未免略有简化之嫌。所以最近已有社会学家从比较长远的历史过程中去分析知识分子的问题。知识分子并不是工业革命以后的新事物,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知识阶层,因而也各有其特殊的知识分子的问题。 而从另一方面看,知识阶层虽有中外古今之异,但未尝不具备若干通性。以目前的研究业绩来说,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特别是知识社会学家) 的注意力依然是偏重在近代方面,尤其是近代西方的知识阶层。因此对于通性方面,尚不能遽下“结论”。 在这种情形下,研究近代以前非西方社会的知识阶层便更显得是当务之急了。
(一)近代有关“士”之起源诸说
(二)“封建”秩序的解体与士阶层的兴起
贵族下降为士不仅可从一般的历史趋势推知,而且还有具体的例案可考。孔子弟子中颜回和曾点、曾参父子的家世最便于说明这一点。颜回是最著名的贫士,但是从他的远祖邾武公(字伯颜) 为鲁附庸改称颜氏以后,十四世皆仕鲁为卿大夫。至颜回的祖父则已降为“邑宰”,可能已是“士”了。
《说苑·建本》篇说“曾子(参) 艺瓜,而误斩其根。曾皙(点) 怒,援大杖击之” 。《立节》篇又说“曾子衣弊衣以耕” 。曾氏父子显然都是庶人。然《世本》却说曾皙是鄫太子巫子孙。明儒陈士元遂据此谓曾氏“四世皆贤,不仕于鲁,以取鄫故” 。则曾氏正是史墨所谓“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的一个绝好例证。至于孔子本人从“三后之姓”(殷) 沦为“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的士,那更是尽人皆知的了。
庶人的上升对传统的“士”阶层所造成的激荡更为严重。到了春秋末叶,士庶的界限已经很难截然划分了。 上引赵简子“庶人工商遂”及《邾公华钟》的“台宴士庶子”之文都说明春秋晚期庶人已有正式的上升之途。但庶人之上升并不尽由于战功,至少下逮春秋、战国之交,庶人以学术仕进者已多其例。《吕氏春秋·尊师》篇说:
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
此六例证是否完全可靠是另一问题,但它们所显露的时代通性则不容置疑。
……
春秋、战国之际农人可以上升为士,尚可证之于《管子》和《国语》。《管子·小匡》篇在“农之子常为农”之下说道:
朴野而不慝(注:农人之子朴质而野,不为奸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注:农人之子,有秀异之材可以为士者,即所谓生而知之,不习而成者也。故其贤足可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注:以农民能致粟,又秀材生焉。故圣王敬畏农而戚近之)。
这里显然是说农民之秀出者可以上升为士。而且此所谓士,已不是武士,而是“仕则多贤”的文士了。
……
四民社会的成立必须以士从最低层的贵族转化为最高级的庶民为其前提。这一前提是到了春秋晚期以后才存在的。《榖梁传》“成公元年”条云:
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
《榖梁》著帛较晚,自是四民制度成立以后的见解。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士民”这样一个新的名词,把士的社会身份正式地确定在“民”的范畴之内,这是春秋晚期以来社会变动的结果。由于贵族分子不断地下降为士,特别是庶民阶级大量地上升为士,士阶层扩大了,性质也起了变化。最重要的是士已不复如顾炎武所说的,“大抵皆有职之人”。相反地,士已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而进入了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 。这时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却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待着他们。在这种情形之下,于是便有了所谓“仕”的问题。“仕”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就业问题,至少对于一部分的士而言,其中还涉及主观的条件和客观的形势。子夏说: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学而优”是“仕”的主观条件。主观条件不具备是不应该“仕”的,所以孔子使漆雕开仕,漆雕开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听了很高兴 。因为漆雕开度德量力,学而未优不肯就仕。孔子又赞叹道: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有道、无道则构成“仕”的客观形势。孟子也非常重视“仕”的问题: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曰:“……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前半段说“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乃指古代封建制度下“大夫士”的“士”,而“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则已指四民之首的新“士”了。所以合孔、孟的言论而观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仕”纵使不是春秋战国之际才产生的新观念 ,它至少也是伴随着“士民”而来的新问题,“士民”的出现是中国知识阶层兴起的一个最清楚的标志。
(三)士的文化渊源
前引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说古代只有武士,至孔子殁后才逐渐有文士的兴起,所以文士是从武士蜕化而来的。这个说法在今天已差不多成为定论了,但细按之,其中问题仍然不少。首先,顾氏此文即陷入严重的自相矛盾,因为他接着又说战国之世“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这就是所谓“儒”和“侠”的对立。儒、侠对立又是怎样产生的呢?顾氏说:
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惮用力者归“儒”,好用力者为“侠”,所业既专,则文者益文,武者益武,各作极端之表现耳。
这里显然与前文有两重矛盾:第一,文士与武士既属分途发展,则自然不能说武士蜕化为文士了。第二,此处云“古代文、武兼包之士”和开始的“古代之士皆武士”更显然不能并存。侠的问题不在本篇讨论范围之内,但就文士的起源而言,顾氏的后一种说法倒是比较接近真实的。由于这个问题也是古代知识阶层之兴起的一个环节,我们必须对它加以澄清。
以古代之士皆武士,其最有力的根据是说古代的学校为军事训练的所在。顾氏所引金文及其他先秦资料都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的,这个观点近来更因杨宽关于古代大学的研究而加强。杨氏认为“西周大学的教学内容以礼乐和射为主要”,他说:
当时贵族生活中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有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但是,因为“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他们是以礼乐和射御为主的。
接着他更举证说明,西周大学教师称“师氏”,即因最初的大学教师是由称“师氏”的高级军官担任之故,不但如此,古时教师尊称为“夫子”也起源于“千夫长”、“百夫长”之类的军官名称。所以西周大学是以军事训练为主,其目的在于培养贵族军队的骨干。
杨氏的说法并不算错,但显然没有能够从全面来考虑问题。我们固不必相信后世“周尚文”之说,但孔子已明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周代虽然不能不重视武力,但其特色正在能“文之以礼乐”。以古代之士皆武士者都特别着重“射礼”,其实“射”在周代绝不完全是军事训练,其中含有培养“君子”精神的意味。所以孔子说: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又说:
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为礼乐教育的一部分,不是军中的武射,这是很明白的。而且孔子明说这是“古之道”,可见并不是春秋时的事,西周想已如此。 因此我们绝不能因周代学校有习射之事而断定其必为军事训练之地。总之,周代贵族子弟的教育是文武兼备的,以具体科目言,则六艺之说大体可信。《礼记·王制》云: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王制》虽出汉代儒者之手,且所言亦过于理想化,但此条却有其先秦的根据。《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条记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之事云:
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乃使郤縠将中军。
晋文公要找一位元帅,赵衰竟推荐“说礼乐而敦诗书”的郤縠去担任,而晋文公也毫不迟疑地接纳了。这个例子最足以说明古代贵族所受的教育是文武合一的。纵使统领三军的元帅也必须精于诗、书、礼、乐,这更是“郁郁乎文哉”的具体表现。
春秋是古代贵族文化的最后而同时也是最高阶段。顾炎武论春秋与战国之不同,说道: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顾氏所说的春秋时代这些特色其实都可以用礼乐两个字来包括。春秋时代一方面是所谓“礼坏乐崩”,一方面却又是礼乐愈益繁缛。这正是一事之两面,所以虽在战阵之上也不能不讲究礼乐。宋襄公“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固然成为后世的谈柄,但却正是当时尊礼重信的一个最极端的例子。 所以这些礼乐,都和诗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顾氏所举的“宴会赋诗”更说明当时国际政治必须具备高度的文化教养。根据近人统计,《左传》引诗一百三四十处,其中关于卿大夫赋诗的共三十一处。 故春秋时倘非深于诗、书之教的人是不敢在国际宴会的场合出现的。晋文公流亡时和秦伯相会的一幕便是最好的例证。史称秦伯将享重耳,
子犯曰:吾不如赵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秦伯)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我们在前面看到赵衰推重郤縠的文化修养,现在我们知道赵衰本人也是一位对诗、书、礼、乐极有造诣的专家,子犯推重赵衰之“文”,绝非普通客套,而是因为此会足以决定重耳未来的政治命运。则“文”在实际政治上的重要性,可以想见。
春秋早期的礼乐远不如后期的复杂,所以贵族中尚不乏文武兼资之人。后期则贵族中已多不知礼之人了,《左传》昭公七年条云:
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即何忌)与南宫敬叔(即说)师事仲尼。
像孟僖子父子这样的贵族居然已不能知礼,而必须向“士”阶层中的孔子去学礼了,可见得贵族时代已到了曲终雅奏的时候了。孔子由于“少贱,故多能鄙事”,遂成为当时的博文知礼的专家。又由于孔子“有教无类”,他遂将古代贵族所独占的诗书礼乐传播到民间。但孔子已无法做文武兼资的通才了。《左传》哀公十一年云:
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
这个故事透露出知识阶层兴起的时代背景。所以,严格地说,文士并不是从武士蜕化而来的,他们自有其礼乐诗书的文化渊源。关于这一点,在下节“哲学的突破”中可以获得充分的说明。
(四)“哲学的突破”
以上我们从社会根源上清理了古代士阶层兴起的一些问题。我们的历史追溯工作大体上止于孔子出现的前夕。以下论士阶层的发展将始于孔、墨学派的建立,而终于秦代的统一。
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并不能完全从社会变迁的方面获得理解。顾名思义,知识阶层的主要凭借自然是它所拥有的“知识”。因此我们必须从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上来讨论这个问题。
……
帕氏认为古代四大文明都曾经过“哲学的突破”,这是不成问题的。他又认为每一“突破”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故所表现的方式与内涵皆各异,这也是一个有效的论断。但由于帕氏对古代东方的历史知识缺乏深度的了解,因此他对古希腊和以色列的解说甚为明确,而言及印度与中国之处则不免失之笼统,而尤以中国的部分为然。尽管他对古代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而确定的解说,他所提供的比较观点却有助于我们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整理。
我们已指出,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是针对古代诗、书、礼、乐所谓“王官之学”而来的。最先兴起的儒、墨两家,便是最好的说明。孔子一方面“述而不作”,承继了诗、书、礼、乐的传统,而另一方面则赋予诗、书、礼、乐以新的精神与意义。就后一方面言,孔子正是突破了王官之学的旧传统。墨子最初也是习诗、书、礼、乐的 ,但后来竟成为礼乐的批判者。就其批判礼乐言,墨子的突破自然远较孔子为激烈。 其余战国诸家也都是凿王官之学之窍而各有其突破。故刘歆说:
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
刘歆的九流出于王官说,分别以察,虽多不可通,但汇合以观则颇有理据,和《天下》篇所云“道术将为天下裂”者,正相通流。我们今天必须从“哲学的突破”的观点来重新体会其含义。
帕森思谓中国古代的“哲学的突破”最为温和,主要是针对着儒家而言。儒家守先以待后,寓开来于继往,所以斧凿之痕最浅,无论就“突破”的过程或“哲学”的内涵而言皆然。事实上,其他各家的突破,与儒家相较虽甚激烈,但全面地看,仍然是相当温和的。这种温和的性格至少一部分源于诸子立言所采取的“托古”的方式。
“哲学的突破”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极密切的关系。因为突破的结果是帕森思所谓的“文化事务专家”(specialists in cultural matters) 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显著的集团。他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最初型态。 韦伯曾郑重地指出亚洲几个主要大宗教的教义都是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这些知识分子也像古希腊各派的哲学家一样,不但社会地位较高而且具有类似古希腊哲学家的学术训练。他们是宗教(如印度) 或伦理(如中国) 的教义的承担者,但他们的活动主要是学术性的,如“柏拉图学院”之例。对于当时的官方宗教,他们的态度是不即不离的——或者不加理会或赋以哲学新义。另一方面,官方宗教对这些知识分子所发展的新教义也往往有所简别,有的被尊为正统,有的被斥为异端。
……
近代学者曾追问过“儒家学说何以适应秦、汉以来的社会” 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不能有简单的答案。我们现在不妨换一个问题,即孔子曾对传统的礼乐赋予新的解释,何以并没有引起当时鲁国贵族的强烈反感?而孟僖子还特别要他的儿子去向孔子学礼?我们认为这一点是和上面所说的中国“哲学的突破”的温和性格分不开的。但此中的关键尚不仅在于孔子个人之善于融合新旧,而更在于三代以来所谓王官之学的礼乐传统一直是在因革损益中演进的。孔子曾说: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孔子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所作的断案,现在依然有效。夏代的历史虽然至今仍不能说已得到地下资料的充分证明,但考古学家中已颇有人采信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之说了 。孔子一方面“从周”,一方面又说:“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这种温和的“突破”在性格上恰与三代不断损益的文化传统若合符节。当这一传统面临“礼坏乐崩”的危机时,儒家的“维新”路线为它提供了一个最容易适应的变革方式。相反地,墨家否定礼乐的激烈态度则与此传统最为格格不入。所以在先秦诸子之中,儒、墨虽一度并号“显学”,但在长期的竞争之下儒家终于取得“正统”的待遇,而墨家却被摈于“异端”之列了。
(五)“士志于道”——兼论“道”的中国特征
“哲学的突破”造成王官之学散为百家的局面。从此中国知识阶层便以“道”的承担者自居,而官师治教遂分歧而不可复合。先秦诸学派无论思想怎样不同,但在表现以道自任的精神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章学诚说得最清楚:
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夫礼司乐职,各守专官,虽有离娄之明、师旷之聪,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传,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则人人皆以为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之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
章氏站在儒家的立场上特别偏袒孔子,说“夫子述而不作”,“不敢舍器而言道”。其实孔子也是喜欢“言道”的,和其他诸子并无显著的分别。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道统”观念远在古代“哲学的分裂”之际已露其端倪,虽则当时尚没有“道统”这个名词。
知识分子以道自任的精神在儒家表现得最为强烈。孔子说: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这番话当然是以士为对象而说的,因为他在别的场合还说过: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这些说法意思都相通,都是在强调士的价值取向必须以“道”为最后的依据。所以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 后来的士是否都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另外的问题,但由于孔子恰处在士阶层兴起的历史关头,他对这一阶层的性格形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的弟子曾参便曾发扬师教,对“士志于道”的精神从正面加以阐释。他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宋儒“曾子传道”之说,虽不足采信,但他们之所以为此说则正是根据上引曾子这一类的议论。
儒家的理想主义到了孟子的手上更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孟子把士与道的关系扣得更紧密。他说: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
旧题孔奭疏云:“《论语》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同意。” 疏语大体不误,但孟子的说法似乎比《论语》原文更为积极了。孟子论士和道的关系见于下面一节文字: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
这番话也是对上引孔子“士志于道”及《述而》篇“志于道”一语作更细密的发挥。 仁义为儒家之道,故志于仁义即志于道。
孟子即扣紧孔子士与道合一之教,因此对于士的进退出处的大节,所论亦益能入细。他说:
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士能不论穷达都以道为依归,则自然发展出一种尊严感,而不为权势所屈。所以他说:
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尽心上》)
孟子在这里已正式揭出道尊于势的观念,后来理学家讲理尊于势便是继承了孟子的精神。 孟子所谓“古之贤士”其实也并不甚古,因为这种以道自任的士是“哲学的突破”和知识阶层兴起以后的新人物。古代封建制度之下的“士”大抵都是“有职之人”,岂能有所谓王公“不得而臣”之事哉!
在“仕”的问题上,孔子已强调知识分子所当考虑的乃是“道”的得失而不是个人的利害。此即所谓“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下逮孟子之世,仕的问题更为普遍而迫切,因此孟子对于士的去就便定下了一套明白而具体的规范。在答复“古之君子何如则仕”的问题时,他说:
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事实上,孟子最注重的只是第一项的去就,即“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与否。第二项已经是面对当时的现实,在原则上打了折扣,不过仍希望保住士的起码尊严罢了。至于最后一项则根本谈不上“就”。接受君主的暂时周济,以免于饿死,终究还是要“去”的。所以顾炎武解释此句:
免死而已矣,亦则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孟子是一个乐观而积极的人,他对新兴的士阶层的理想主义抱有极大的信念。他毫不迟疑地说: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
我们知道,“恒”是孔子所非常重视的一种德性,因为它是很难得的,故说:“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论语·述而》) 又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论语·子路》) 现在孟子则认为只有士可以摆脱个人经济基础的限定而发展他的“恒心”。这可以看到孟子对当时新兴的士阶层的期待之高。孟子的看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近代社会学家也曾指出,由于知识阶层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阶级,因此它始能独持其“思想上的信念”(intellectual convictions) ,这一“思想上的信念”之说正好是孟子所谓“恒心”的现代诠释。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让我们看看他对士与道的问题的意见。首先必须指出,在荀子的时代,儒家与其他各派在政治上的竞争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因此他推崇儒家与排斥诸子,也是着眼于现实政治,而与孟子之仅在思想层次上距杨、墨者有所不同。他在《解蔽篇》中批评了各家皆“蔽于一曲”之后,独许孔子为得“道”之全。其言曰:
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绩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
然则孔子之“道”的功用如何呢?他说:
曰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则合于道人而不合于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与道人论非道,治之要也。
可证荀子论“道”归之于“治”,并且主张在政治上“禁非道”,即孔子以外之各种“道”。荀子希望用儒家之道来垄断政治,其意又见于《儒效篇》。《儒效篇》说: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天下之道毕是矣。乡是者臧,倍是者亡。乡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
杨倞注此段,说“是”皆谓“儒”也,是可信的。《儒效篇》的主旨是要说明“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由于荀子处在大一统政府建立的前夕,知识分子多少已感到政治上的低气压,所以荀子对“道尊于势”的观念似不及孟子所持之坚。但他并没有丧失儒家的基本立场,故仍以儒者之所以可贵即在于其所持之道。更重要的,他虽偶有敷衍世主的尊君之说,然论及君臣关系却一再强调“从道不从君”的原则 。这仍然可以看作是“道尊于势”的观念在一种新的政治形势之下的委婉表现。
荀子对于士当以道自任与自重一点,也依然守住了儒家传统。《大略篇》有云:
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食则饘粥不足,衣则竖褐不完。然而非礼不进,非义不受。……子夏贫,衣若县鹑。人曰:“子何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
《大略篇》是弟子杂录荀子之语,则荀子平时的持论可想而知。《尧问篇》则借周公之口曰:
夫仰禄之士,犹可骄也,正身之士,不可骄也。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
杨倞注云:“赖守道之士不苟徇人,故得纲纪文章常存也。”更可见荀子于士与道不可须臾离之义,守之甚严。
王侯不得骄士之说,在战国晚期甚为流行,大概是当时游士极力宣传以自抬身价的结果。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荀子把士分为“仰禄之士”与“正身之士”两类,并说王侯不妨对前者骄傲。这是士阶层高度分化的一种反映。士阶层的分化可以说是自始即然,早在孟子的时代已有“与民并耕而食”的许行(《孟子·滕文公上》) ,也有以“以顺为正,妾妇之道”的公孙衍和张仪(《孟子·滕文公下》) 。但到了荀子之世,不讲原则而一意猎取富贵的游士在数量上更是庞大了。 荀子所谓“仰禄之士”正是指着这种人而言的。因此孟子尚笼统地讲“士”,而荀子却不能不对“士”作进一步的划分。王先谦曾正确地指出,荀子之书分士、君子、圣人为三等,《修身篇》、《非相篇》、《儒效篇》、《哀公篇》诸篇都足为证。 换句话说,根据荀子对知识分子的分类系统,“士”乃是最低的一级。故普通的“士”尚不足以尽“道”。 足以担当“道”者必须是“君子”或“士君子”。 《致仕篇》说:
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
我们试把此处“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之语和《儒效篇》“圣人也者,道之管”一段联系起来看,便可知荀子所谓“君子”绝非一般的知识分子,而是特指有学问、有修养的“儒士”。总之,由于所处的时势不同,荀子笔下之“士”其流品已甚杂,不可与孔子所言“士志于道”之“士”等量齐观,只有荀子所说的“君子”或“士君子”才与孔、孟所称道的“士”约略相当。明乎此义而反求之荀子之书,则可知荀子仍守孔子“士志于道”之见而未变。所不同者,荀子之世,儒家因与其他学派在政治上的争持正烈,故“士志于道”的观念也相应而变得高度地政治化了。
以上我们通过儒家的文献对古代士阶层的行为规范作了一个大体的勾画。我们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孔子及其门徒对中国士阶层的性格的形成,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受了资料本身的限制——古代儒家的著作保存得比其他学派都完备。但上述的行为规范却不是儒家的专利品,它可以一般地适用于当时新兴的士阶层。墨子的若干议论便足以证实这一点。
墨子是主张“尚同”的,即要人人上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因为唯有天子“壹同天下之义”之后,天下才能大治。 依照这个理论,则“道”与“势”必须是合一的,因而自不能容许儒家那种“道”、“势”两分的说法,更不必说什么“道尊于势”了。但此在墨子亦不过是就究极之义言之,墨子并不承认当时实际上已有一位“壹同天下之义”的天子。所以,“尚同”说和孔子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最多也不过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认真地说,在墨子的心目中,只有接受了他所承继的“先王之道”的“天子”才有资格“壹同天下之义”。在这位“天子”不曾出现以前,墨子和孔子一样,是把“道”承担在自己的身上的。《尚同下》说:
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天下既已治,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故当尚同之为说也,尚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诸侯,可而治其国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小用之,治一国一家而不横者。(按:孙诒让注:窕,不满也;横,充塞也。)若道之谓也。……意独子墨子有此,而先王无此其有邪?(孙诒让曰:疑当作“无有此邪”,“其”字衍。)则亦然也。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于先王之书也。
这段话最足以证明墨子的“尚同”之道本是他所“独有”,不过他托古于“先王”而已。
墨子另一有名的理论是“尚贤”。其实“尚贤”即是“尚士”,“贤”与“士”在《墨子》可以互训。故《亲士》篇开宗明义云: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怎样才能得贤士呢?什么样的人才配称作贤士呢?墨子说:
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
可知得贤之道便是在政治上重用他们,而所谓“贤”便是有道德、学问、技能的人才,也就是当时新兴的士。
墨子主张士人大量地参政,其着眼点也在于“道”的实现,固与儒家立场相去不远。所以他说:
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按:据孙诒让引孔广森云:承,丞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士既为道的承担者,则士之进退出处亦不可不慎。儒、墨两家在这种大关键上并不是背道而驰的。《墨子》中《修身》与《贵义》两篇便是针对士的立身处世而发的。《贵义》篇云: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愠,是犹欲其墙之成,而人助之筑则愠也。岂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今闻先王之遗(按:“道”之误)而不为,是废先王之传也。
同篇并记载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故事:
子墨子仕人于卫。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对曰:与我言而不当(孙诒让云:“当”疑作“审”)。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过千盆,则子去之乎?对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则非为其不审也,为其寡也。
这个故事也许是后起的,但至少表示墨家主张士之仕当以义为根据,不当争待遇之多寡。这和孟子论去就,义相足而不相悖。《公孟》篇也有一个故事说:
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身体强良,思虑徇通。欲使随而学。子墨子曰:姑学乎,吾将仕子。劝于善言。而学其年(“其”即“期”字),而责仕于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今子为义,我亦为义,岂独我义也哉。子不学,则人将笑子。故劝子于学。
这正与孔子所谓“三年学,不志于穀,不易得也”(《论语·泰伯》) 如出一辙。儒、墨两家先后兴起,导夫诸子之先路,所言之“道”不同,而所表现“士志于道”的精神则一。这是很可玩味的。
如上所陈,先秦的士以“道”自任而他们之受到时君的尊重主要也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道”(参看下文)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追问,他们的“道”,从比较文化史的观点看,究竟具有何种特征?我们强调“比较文化史的观点”,是因为就本文的宗旨说,我们对先秦诸家之“道”毋须分求其异,但当总观其同,以凸显其与其他古代文化中之“道”的分歧所在。中国知识阶层的特殊性格,以及中国思想进程所采取的独特路向,都多少可以由此而获得说明。
由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突破”是以“王官之学”为其背景,而且“突破”的方式又复极为温和,因此诸家论“道”都强调其历史性,即与以往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韩非子·显学》篇云:
世之显学,儒、墨也。……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
儒、墨两家最先起,而皆自溯其“道”至远古。 这一点最可表示儒、墨在“王官之学”解体之后,极力要争取“道统”上的正宗地位。他们并不承认“道”是他们创建的,换言之,他们的“道”都是“法先王”而来的。 不但先起的儒、墨两家如此,其他各家之“道”也无不强调其历史性。《淮南子·修务训》篇说: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
《淮南子》之说一方面指出诸家之“道”皆“托古”以争正统,另一方面,更透露出战国君主重视诸家之“道”的一个原因便在于它源自古代的传统。我们有理由相信,战国时代的各国君主多少都感到需要一套具有历史渊源的理论(即所谓“道”) 来强化他们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这显然对当时诸子的“托古”颇具激励的作用。 甚至战国时一般的游士也都以“托古”为干禄的手段。汉初的司马季主说:
公见夫谈士、辩人乎?虑事定计,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说人主意,故言必称先王,语必道上古。虑事定计,饰先王之成功,语其败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夸严(按:王念孙云“严”读为“譀”即“诞”也),莫大于此矣。
……
中国古代“道”的另一特征,我想称它为“人间性” 。这里所谓“人间性”当然也是从比较文化史的观点来说的。印度和以色列的宗教传统虽然也离不开世间的问题,但是世间问题在这种传统中毕竟是以超世间的形态出现的。换句话说,便是“把世间的问题变成神学的问题” 。古希腊思想在“哲学的突破”的前后曾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人间性”,即辩者(Sophists) 和苏格拉底将古希腊人的哲学兴趣从自然界转移到人生界。但古希腊的哲学传统是从对自然界的好奇与探索开始的,这一向自然界追求永恒规律的训练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思想家对人生问题的处理方式。当他们的目光转移到人生问题时,他们同样要在人的内在宇宙中寻找不易之则。这就不免将人生界客观化而与自然界同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了。因此柏拉图的伦理学与政治学都是模仿当时的医学而建立起来的。
相形之下,中国古代之“道”,比较能够摆脱宗教和宇宙论的纠缠。中国没有古希腊那种追究宇宙起源的思辨传统。孔子以前中国有讲吉凶祸福的“天道”观 ,那是一种原始的宗教思想。但是这个天道观在“哲学的突破”前已经动摇了。《左传》昭公十八年 载:
裨灶曰:“不用吾言(按:指欲用瓘斝禳火),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
这是一个最有名的故事,正可用来说明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突破”的过程中,从“天道”转向“人道”是一个关键性的发展。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态度便是从这里滥觞出来的。墨子好言“天志”,这是古代的原始宗教思想。但是我们细读《天志》三篇,即可见墨子的注意力仍在人间的“兼爱”,其中并无“天国”的观念。他不过是假传统的旧“天道”以加强他的新“人道”而已。后起的道家系统地发展了崭新的宇宙论。 稍有提高“天道”的倾向,故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篇》) 但庄子仍有《人间世》和《应帝王》之作,不但不离乎人间,并且不忘情于政治。 所以,全面地看,中国古代之“道”的人间性是非常明显的。
中国“道”的人间性更有一个特点,即强调人间秩序的安排。司马谈说得最明白: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可见先秦诸子,包括讲“坚白同异”的名家在内,最后都归结到治国、平天下之道上去。 “道”足以安排人间的秩序,这又是当时的有“道”之士所以受到各国君主的礼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六)君主礼贤下的“不治而议论”
必须指出以上所引几段材料都出自秦汉以下,显然是经过战国晚期以来游士的润饰和夸张,所以个别故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尤其据《吕览》所言,魏文侯已完全接受了“道尊于势”之说,这绝不是当时信史。但这些材料却共同透露出一个重要的消息,即魏文侯对于贤士分为两类,而礼遇的方式不同。一类是肯居官受禄之士,如翟璜、李克诸人,他们和文侯是正式的君臣关系。一类是不肯居官受禄之士,如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个人,他们和文侯的关系则在师友之间 。这一个大分别在先秦材料中得到印证,则是可信的。《孟子》云:
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 (《孟子·万章下》)
孟子出于子思学派 ,此说纵有特别突出子思之嫌,但所言之大体分类绝不可能是向壁虚造的。足见战国时君主与士之关系确有师友与君臣之两类,虽然其间的分别未必即如记载所言的那样清楚。
鲁缪公礼贤的情形也与魏文侯有相似之处。《孟子》曰:
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孟子·万章下》)
这条记载可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叙述事实,即鲁缪公表示要和子思为友,而子思不悦,因为他要以师自居。后一部分君臣、德位之说则是孟子的借题发挥。发挥的部分可以不论,就事实的部分说,好像缪公与子思之间略有冲突。缪公自以为礼贤下士,故不视子思为臣,而欲与之友。子思却并不以此为足,坚持正师弟之谊。孟子又告诉我们另一个故事:
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台无馈也。(《孟子·万章下》)
赵岐注有云:
从是之后,台不持馈来,缪公愠也。愠,恨也。
更可知这两个人之间确因师友之争而发生了裂痕。《汉书·艺文志》在“子思二十三篇”条下注道:
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
则后世儒家相传,仍坚持子思为鲁缪公之师。更有趣者,淳于髡说:
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孟子·告子下》)
而赵岐注云:
鲁缪公时,公仪休为执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子之孙,伋也。二人为师傅之臣。
赵岐用“师傅之臣”来注原文的“臣”字,是增字解经的典型例证。但可见子思为鲁缪公师之说,在汉儒已成为定案了。孟子又尝说:
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孟子·滕文公下》)
赵岐注曰:
孟子言魏文侯、鲁缪公有好义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则可以见之。
则鲁缪公礼贤与魏文侯齐名,大概不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所可惜者,由于史料残阙,又复经后人润饰,真相已难恢复。据上引资料推断,鲁缪公至少对子思、泄柳采取了一种“友而不臣”的态度。至于子思等在鲁缪公之朝究竟发挥了何种“士”的功能,现在已无从知道了。
子思以后,士阶层高自位置的风气愈烈,于是出现了决不肯与政治权威妥协的一类人物,如齐国的陈仲便是最好的榜样。《战国策·齐策》记赵威后对齐使之言曰:
于陵子仲尚存乎?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孟子与陈仲同时,曾称许他为齐国之士的“巨擘”,但反对他的激烈思想。 这种上不臣于王、中不友于诸侯的极端知识分子在当时统治者的眼中已具有政治上的高度危害性,以致使赵威后动了杀心。其情况又远较鲁缪公对子思之仅止于“愠”为严重了。
士阶层中产生了一批以道自负之人,不甘自贬身价去入仕。温和者尚自许为王侯的师友,激烈者则拒斥一切政治权威。
……
以上有关稷下之学的几条材料在细节方面彼此颇有出入,但它们在说明稷下先生的功能这一点上却完全是一致的,即所谓“不治而议论”。《盐铁论》“不任职而论国事”一语当然是“不治而议论”的确诂 。稷下学宫的出现不但是先秦士阶层发展的最高点,而且更是养贤之风的制度化,其意义的重大是无与伦比的。
我们在前面曾看到,在魏文侯和鲁缪公时代,“道”与“势”之间已发生了一种微妙而紧张的关系。鲁缪公和子思之间的纠纷尤其是这种关系的具体说明。下逮齐宣王之世,各国竞争益烈而士之气焰也愈张。世主既不能屈贤士为“臣”,又不能和他们永远维持一种无形式而不确定的“师友”关系。稷下先生之制便是适应这种形势而创设的。“游稷下者称学士,其前辈称先生。” 这正是齐王表示待他们以“不臣之位”之意。《孟子荀卿列传》又称“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列与例通,其义为比,是说稷下先生爵比大夫。故同传又谓淳于髡“终身不仕” 。稷下先生不算入仕,尚可以田骈为证。《战国策》云:
齐人见田骈(注:齐处士)曰:闻先生高议(义),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曰:子何闻之?对曰:臣闻之邻人之女。田骈曰:何谓也?臣邻人之女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今先生设为不宦,訾养千钟,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矣。田子辞。
这个故事本身是否可信,是另一问题。但田骈明是稷下先生而齐人说他“不宦”,则列大夫和齐王的关系不是君臣,而在师友之间,从此可知矣。
稷下先生“不治”、“不任职”,即不在官僚系统之中,所以依然能保持“士”的身份。这可以看出当时的士已发展了群体的自觉,而道尊于势的观点也相当的普遍了。 但同样值得重视的则是稷下先生的“议论”。他们的议论当然都是本于自己所持之“道”。由于他们的“道”具有历史性与人间性(特别是政治性) 的特色,他们的议论从来就不是一般性的,而具体地表现为“言治乱”、“议政事”或“论国事”。
“议论”并不完全相当于现代“讨论”、“商议”的意思,其主要含义近乎我们所说的“批评”。孔子曰: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条云: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这段话不但使我们确知“议”和“论”都是批评,而且也说明了孔子“庶人不议”一语的历史背景。孟子曰: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
此处所言“横议”更是“批评”之意。但孟子的时世已与孔子不同。孔子时,“士”刚刚突破封建体制,成为“四民之首”,士庶的关系密切,因此孔子说“庶人不议”,其中即有“士”在。《国语》“庶人传语”之说在《左传》则为“士传言”,足为佐证。 从孔子到孟子这一个世纪之中,士阶层的发展最为惊人。一方面,士已成为一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集团,另一方面此集团本身又发生了学派的分化。所以孟子要骂儒门以外的“士”为“横议”了。
《淮南子·俶真训》说: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于是博学以疑圣(按,王引之云:疑读曰拟),华诬以胁众,弦歌鼓舞,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
《淮南子》的撰者以道家为主,故攻击儒、墨诸派。其中“列道而议”之说正是指“道术将为天下裂”以后的“处士横议”。可见汉初的人对于战国知识分子各持其“道”以批评时政的风气仍然认识得十分亲切。事实上,说这个话的人本身也依然在同一风气的鼓荡之中。《盐铁论·晁错》篇载御史大夫桑弘羊之言曰:
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谋叛逆,诛及宗族。
此处儒、墨当然是泛指各学派而言。由此不难看出,汉代当政者对于“处士横议”是多么的深恶痛绝。
我们明白了“议论”的含义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就更能懂得何以稷下学兴盛之世是古代士阶层的黄金时代了。……稷下学宫虽仅昙花一现,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则是永恒的。因为议论的自由同时也刺激了思想学术的成长。先秦所谓“百家争鸣”的时代主要是和稷下时代相重叠的。在这个时代中,不但齐国尊贤,其他各国也莫不如此,但不及稷下之著名而已。驺衍为稷下先生,但《史记》又说他“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 。举此一例,可概其余。纵其中故事不尽可信,而一时风尚,固不难察见。等而下之,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四公子的养客也适发生在这个时代的晚期,这绝不是偶然的。史称稷下先生千有余人,但姓名可考者不过十六七人。然而就在这寥寥十余人之中,《天下》篇所论之古代十二子中,名列稷下者便有五人(宋鈃、尹文、彭蒙、田骈、慎到) ,几居其半。荀子身列稷下,其《非十二子篇》评论战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六派思潮,与稷下有关者凡三派四人(宋鈃、慎到、田骈、孟轲) 。以人数言是三分之一,以派别言则恰好一半。稷下学宫“不治而议论”的制度在先秦思想史上所发生的影响之大即此可见。
……
我们在前面曾指出,稷下学宫的创建是魏文侯、鲁缪公的养贤办法的形式化、制度化。我们现在要更进一步说明,博士制度则是稷下学宫的新发展。
王国维《汉魏博士考》云:
博士一官,盖置于六国之末,而秦因之。《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博士,秦官。《宋书·百官志》:博士,班固云秦官。史臣案:六国时往往有博士。案:班、沈二说不同。考《史记·循吏传》:公仪休,鲁博士也。褚先生补《龟策传》:宋有博士卫平。《汉书·贾山传》:祖袪,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沈约所谓六国时往往有博士者,指此。……公仪子,缪公时为鲁相,时在战国之初。卫平在宋元王时,亦与孟子同时。疑当未必置博士一官。《史记》所云博士者,犹言儒生云尔。惟贾袪为魏王博士弟子,则六国末确有此官。且教授弟子,与秦、汉博士同矣。至秦之博士,则有定员……多至七十人。
王氏据史传断定博士之制起于六国是正确的。但其中尚有待发之覆。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说:
《说苑·尊贤》篇称博士淳于髡,《五经异义》谓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是也。然他书皆称稷下先生,不称博士。二者盖异名同实。故汉祖拜叔孙通为博士,而号稷嗣君,此谓其嗣风于稷下。郑康成书赞亦谓我先师棘下生孔安国,棘下即稷下也。安国为汉廷博士,而郑君称之为稷下生,故知博士与稷下先生异名同实。晚汉犹未堕此义。……《史记·田齐世家》谓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续志》:博士,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通古今,承问对,此即不治而议论也。……博士既承问对,则易涉于议政。
钱宾四师抉出了博士与稷下先生“异名同实”这一重要事实,然后博士制度的源流始灿然明备。在王、钱两先生的考证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而阐释博士制度的流变在士阶层发展史上的意义了。
博士置于六国之末,而且是嗣风于稷下,这两点毫无可疑。但是博士虽相当于稷下先生,博士制度却不是稷下制的简单重复,其间已有重要的变化。博士制与稷下制最大的不同有二。第一,前已言之,稷下先生命曰列大夫,是爵比大夫,不在正式官制之中,故时人谓之“不仕”或“不宦”。换句话说,他们根本不是官吏,仍保持着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但秦汉的博士,则是太常的属官,秩比六百石。 博士属之太常,这不但是古代宗教统辖学术的遗意,而且还是官师合一的复古。章学诚说:
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合于一,于是人之学术,不尽出于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而人乃狃于所习,转以秦人为非耳。
准此而论,则秦的博士制度是“以吏为师”的一种制度化。通过博士制的建立,以前自由身份的教书匠(师) 便转化成为官僚系统中的“吏”了。
第二,先秦之士持“道”与“势”相抗,所以他们争取和王侯之间保持一种师友的,而不是君臣的关系。稷下先生便是师友关系的形式化、制度化。“先生”一词在稷下有专称意味。 这是齐王以师友之礼相待,故称先生而不名。稷下为学宫之名,当时君主有立学宫敬礼贤士的风气。《史记》说:
驺子……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战国策·燕策》:
燕昭王……往见郭隗先生曰……敢问以国报仇者奈何?郭隗先生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当时筑学宫、称“先生”是王者待士以师友之道。由“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之说及齐宣王挽留孟子之事观之,则稷下先生与王者的关系决当在师友之间。所以稷下诸贤都是一方面自由讲学,一方面又自由议政。就此点说,他们的稷下宫很像雅典柏拉图和艾索格拉底(Isocrates) 的学院(Academy) 。所不同者,后者乃私立,非官立,更为自由耳。
秦、汉的博士制则与此不同。汉代博士也称“先生”,但系相对于“弟子”、“门人”而言。 博士既为官僚系统中之一员,他和皇帝自然只能是君臣关系。且秩比六百石(本四百石,汉宣帝增秩) ,虽为清要之官,又安能有稷下先生抗礼王侯的气概?社会学家韦伯曾说古代新教义的承担者往往和官方宗教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只有稷下先生的“不治而议论”才合乎这种定义,博士则已被吸收到官方宗教之内,即而不能离了。
……
我们也许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发展史上,博士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七) 私门养客与游士的结局
以上讨论战国时代知识阶层的发展主要集中在这个阶层中流品较高的分子。王侯所礼敬的宾士都是当时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但是战国是一个社会流品逐渐分化的时代,知识阶层本身也不断地在分化中。对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必须另有专篇。 在这最后一节中,我们首先想借着对私门养客的分析来考察一下当时散布在社会中下层的知识分子的一般生活状态。这些流品较低的人物通常都是以“食客”的身份出现的,他们的人数动辄以千计,正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对象。 以整个知识阶层为对象,不再涉及流品的分化了。
《吕氏春秋·高义》篇载墨子之言曰:
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
高诱注“宾萌”曰:“宾,客也;萌,民也。”这个名词尚见于其他先秦文献,其义即是宾客。 “度身而衣,量腹而食”八个字恰是宾客的最准确的定义,使我们懂得何以当时有“食客”这一通称。私门养客大抵止于“足衣足食”,此外似别无经常性的薪给。这个故事不能确定为墨子的时代,但可以用来说明战国中晚期的食客制度。
《史记·孟尝君列传》有一个关于食客冯驩(亦作“煖”或“谖”) 的最著名的故事:
孟尝君置(冯驩)传舍十日,孟尝君问传舍长曰:“客何所为?”答曰:“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缑。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孟尝君迁之幸舍,食有鱼矣。五日,又问传舍长。答曰:“客复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舆。’”孟尝君迁之代舍,出入乘舆车矣。五日,孟尝君复问传舍长。传舍长答曰:“先生又尝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孟尝君不悦。
《索隐》云:“按传舍、幸舍及代舍,并当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集解》也说:“传舍,下客所居。” 我们这里所注意的是故事中私门养客的舍人制度。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食客本身仍有流品的分化,因此舍分三等,食物也随之有别。最高一级的代舍则有车代步,这已是招待食客的极限。故冯驩再作歌,孟尝君便不悦了。传舍长的名称,透露了舍人组织的情况。舍人分等的标准不十分清楚,但总不外能力和贡献。泷川氏的《史记会注考证》引徐孚远的话,说“孟尝君疑冯驩非庸人也,故数问之”。这大概是对的,即冯驩三迁其舍是凭着能力获致的。同传又载狗盗、鸡鸣二客本在最下座,后来立了功,“孟尝君始列此二人于宾客”。这是立功可以升舍的证据。战国食客有下客、少客、上客、宾客种种名目,大体可以断定宾客和上客同义,乃食客中的最高一级。 孟尝君养客之道如此,其他私门亦与此相去不远。平原君的毛遂故事也有助于对舍人制度的了解。第一,平原君要带二十个文武具备的食客,去与楚合纵,仅得十九人,平原君说“士不外索,取索食客门下”,毛遂才有自荐的机会。则“士不外索”是舍人制的一种不成文法。第二,平原君对毛遂说:“今先生处胜门下三年如此矣。左右未有所称颂,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可见舍人制也有某种形式的考绩报告。第三,毛遂立功之后,平原君“遂以为上客”。这更是食客立功升舍的明证。
《史记·春申君列传》说:
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
春申君之例可以说明两点:第一,上舍同时也是用来招待外来上宾的。足见贵族的“上客”或“宾客”所受到的是朋友的待遇。这与国君筑宫以礼贤士,用意并无二致。第二,春申君门下的客也分等级,其上客衣着特别华丽。又《战国策·齐策》:
靖郭君善齐貌辩。齐貌辩之为人也,多疵。门人弗悦。……靖郭君大怒……于是舍之上舍,令长子御之,旦暮进食。
这是靖郭君的客舍分等级之证。“令长子御之,旦暮进食”固是特殊礼数,然仍与“食有鱼”、“出有舆”无大异。同书又曰:
鲁仲连谓孟尝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门(子)养椒亦,阳得子养(原注:此下脱所养人)。饮食衣裘与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于二公,而士未有为君尽游者也。
鲁仲连盛称雍门、阳得二子善养士,而二子之所为仍不出“饮食衣裘与之同”,即止于衣食的供应。
战国晚期,“士”的人数激增,而流品也日益复杂。有些所谓“士”如狗盗、鸡鸣之辈根本不是知识分子,有些则略识之无,也许只能算是“边缘知识分子”(marginal intellectuals) 。这样一大批人散布在许多贵族门下,自然产生了人事管理的问题。私门的舍人制度便是相应于这种新的情势而兴起的。从某种意义来说,私门养客的制度化,正是和国君养贤的制度化平行的。这是古代知识阶层的历史发展的一个侧影。不过私门与王廷究竟不尽同,许多游士只是以托身私门为仕宦的手段。《战国策》云:
孟尝君舍人有与君之夫人相爱者。……君召爱夫人者而谓之曰:子与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又弗欲。卫君与文布衣交,请具车马皮币,愿以此从卫君。
可见这位舍人在孟尝君门下很久只是因为没有等到适当的仕宦机会而已。《史记·吕不韦列传》也说:
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
为了求宦而甘做舍嫪毐人者竟有千余人,则毋怪乎私门之多士矣。《荀子·非十二子篇》说:
今之所谓士仕者(按:王念孙云“士仕当作仕士,与下处士对文”),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也。……今之所谓处士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为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者也,以不俗为俗,离纵而跂訾者也(按:“离纵”谓“离寻常踪迹”,“跂訾”谓“举踵而步”,以示自异于众也)。
荀子在这里所描写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包括做官的和不做官的在内,我们相信是十分真实的。荀子说这番话的意思当然是站在道德的观点上责备他们。我们可以同情荀子的道德观点,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了解何以这些士都不能以“道”自任自重,而竟堕落到“贪利”“嗜势”的地步。
其实荀子的责难当时已由其弟子李斯向他作了最老实的辩解。史载李斯面辞荀子之言有云:
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李斯“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一语固为对战国游士的最确切的形容,其“非世而恶利,非士之情”之说则尤不啻针对上引其师之高论而发。前面已指出,先秦士这一阶层有两大来源,一部分是从旧的“封建”制中游离出来的没落贵族,一部分则是由社会下层浮上去的庶民。无论是贵族下降或庶民上升,他们到了战国的中晚期已贫穷不堪。史籍上足以证明李斯论断的事例,俯拾皆是。举其最著者,张仪“贫无行”,人尝疑其盗璧(《史记》本传) ;范雎“家贫无以自资”(本传) ;虞卿“蹑屩担簦,说赵孝成王”(本传) ;冯驩亦“蹑屩”见孟尝君(《孟尝君传》) ,《战国策》更说他“贫乏不能自存”,愿寄食孟尝君门下(《齐策四》) 。稍后如郦食其“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史记》本传) 。
……
合本传宾客辩士游说,与数千人窃葬事亲观之,吕氏舍人,势力之浩大诚可惊。秦王处置既分三晋籍与秦籍,而秦籍中又以官秩别轻重,皆极见慎重。至于复嫪氏舍人,则颇疑与用人的需要有关。 最近秦律的重要发现更使我们知道秦廷忌惮私门舍人之甚。律云:
使者(诸)侯、外臣邦,其邦徒及伪吏不来,弗坐。可(何)谓邦徒、伪吏?徒、吏与偕使而弗为私舍人,是谓邦徒、伪吏。
律文是说秦使者至国外,如随行官方人员逃走不回国,使者不坐罪,但如使者的“私舍人”不回来,使者便要坐罪了。这显然是怕私门舍人在国外为主人从事政治活动。私门舍人当然不尽是知识分子,但其中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一定是很高的。这尤其以吕不韦的门下为然。
……
历史进入秦、汉之后,中国知识阶层发生了一个最基本的变化,即从战国的无根的“游士”转变为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士大夫”。这个巨大的社会变化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士和宗族有了紧密的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士族化”;二是士和田产开始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可以称之为“地主化”或“恒产化”。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这话只能适用于先秦的游士。汉代的士大夫,至少从汉武帝以后,则很少是没有“恒产”的。“士族化”与“恒产化”事实上是同一社会发展的两面,其作用都是使士在乡土生根。离不开乡土的士当然就不再是“游士”了。
就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战国时代的士几乎没有不游的。 他们不但轻去其乡,甚至宗国的观念也极为淡薄。 其所以如此者正因为他们缺少宗族和田产两重羁绊。苏秦的故事最能够说明这种情况。苏秦最初游说无成而归,“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 。等到后来为“从约长,并相六国”,路过洛阳时则“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苏秦叹曰:
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苏秦不但与宗族关系甚疏,而且他也没有田产,否则他就不会去游宦了。这个故事是否发生在苏秦的身上,我们不敢说。但是战国的游士之中曾有人遭遇过类似的经验,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下逮汉初,游士孤立无援之情尚未大变。请看主父偃的证词:
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
这岂不是苏秦的故事的重演吗?
荀悦论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孙弘族郭解之事曰:
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词,设诈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以树虚誉,以为权利,谓之游行。此三游者,乱之所由生焉。伤道害德,败法乱世,先王之所惧也。国有四民,各修其业。不由四民之业谓之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
荀悦生在汉末党锢之世,“处士横议”再作,感慨之余,乃引申之而有此痛斥三游之论。 细察荀氏“游说”、“游行”两项,前者盖指三晋辩士,后者则谓百家异端,其实皆游士也。按:《战国策》:“王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高诱注曰:“游行。” 游训为行,这是游侠、游士的原始义。现在荀悦论三游之“游”已不强调其背井离乡之原始义,而特指其不安本业之引申义。仅此一端,已可见秦、汉社会与战国大异之所在。中国历史上后来虽仍有“游宦”、“游学”、“游侠”等名目,但“游”的基本性质已变,不再居于主导的地位。古代“封建”秩序崩坏之后,经过春秋、战国的转化阶段,一个“四民社会”的新秩序逐渐在大一统政府之下建立起来了。典型的游士、游侠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其实“游”的原始义和引申义原是不可分割的。苏秦的家人讥笑他说:
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
很显然地,在苏家人看来,苏秦背井离乡去游说,正是不务“本”。但问题在于苏秦所处的是一个“士无恒产”的时代。他如果“治产业,力工商”,有“洛阳负郭田二顷”,那他就不成其为“士”了。只有在秦汉以后宗族与恒产的基础的确立,士的社会活动始不靠“游”来显其特色。所以根据社会史的观点,游士的引申义是比原始义更值得我们重视的。
从“游”字的引申义言,大一统的政府之不能容忍游士、游侠过度活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自由分子无论如何总是一股离心的力量,这和代表“法律与秩序”的政治权威多少是处在相对立的位置。社会学家研究古代帝国的政治系统,曾提出“自由流动的资源”(free-floating resources) 的概念。所谓“资源”,人力和物力都包括在内。帝国的统治者对“自由流动的资源”的问题最为敏感。因为如果让“自由流动的资源”自由发展而不加控制,则将威胁社会的稳定性。但“自由流动的资源”如果过于贫乏,传统的(主要即贵族的) 势力大张,则帝国的行政系统又会为之失灵。因此帝国的统治者必须经常地调节“自由流动的资源”,使之与传统的势力配合,并把这两股力量纳入共同的政治结构与组织之中。帝国的统治是否有效就要看它的调节能力如何。 中国的游士、游侠之类的人物正好为“自由流动的资源”的概念提供了具体的例证。 秦、汉统一的帝国出现,中国知识阶层史上的游士时代随即告终,这是完全不必诧异的。
《云梦秦简》中有《游士律》一条,是有关秦代控制游士的最重要的新发现。兹与其他有关律文一并征引于下,并略加考释,以终吾篇。《游士律》曰:
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
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
第一条是针对外国在秦的游士而设的。“符”即通行证,《汉书·汲黯传》注引臣瓒曰:“无符传出入为阑。” “赀一甲”是“罚一甲”之意。《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訾之人二甲。”高亨曰:“訾借为赀。《说文》:‘赀,小罚,以财自赎……’訾之人二甲,谓罚其人出二甲也。” 秦律中常见赀若干甲或盾之文,当是战国时代需要甲盾之故。 所以这条律文是说外国游士住在某县而没有通行证则罚购一甲之钱,到年底征收。第二条是针对秦籍游士出国者。秦爵二十级,公士一级,上造二级,即最低的两级。“秦制……凡有罚,男髡钳为城旦……作五岁,完四岁,鬼薪三岁。” 城旦分两种,不加肉刑髡𩮜者谓之“完”。 此处不言髡钳,当是完。这就是说,秦士外游者,除削籍外,有公士爵和无爵的人徒役四年,自上造以上的有爵者则徒役三年。判罪当然是就逮捕或出自归案以后而言的。两者相较,秦律似对待本国人较严厉。另有一条律文也与此有关:
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可(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
此处以秦释夏,可知春秋以来,“诸夏”之称入人之深。秦人处西陲仍以夏自居,似有与东方诸国争文化正统的意味。这条律文正是禁秦人外游的,所指即是游士。“主长”者相对于门下、舍人之类而言也。考《韩非子·和氏》篇云:“商君教秦孝公……禁游宦之民。” 而《商君书》亦屡陈斯义。其《垦令》篇则曰:
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勉农而不偷。
可是这些律文在秦行之已久,或竟传自商鞅,亦未可知。《史记·商君列传》说:
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泷川氏《史记会注考证》云:“验,印信传引之类。”其实即是“传”。今秦律有一条说:
今咸阳发伪传,弗智(知),即复封传它县,它县亦传其县次,到关而得。今当独咸阳坐以赀,且它县当尽赀?咸阳及它县发弗智(知)者,当皆赀。
此即关用传出入之“传”,汉文帝十二年曾一度废除者。 此条说从咸阳发出伪造之传,一连经数县至关而发觉,应该罚谁?律文规定无论知与不知,凡伪传通过之县都一样受罚。此条与客舍“无验”虽非一事,而至有关联,且用意完全相通。当日商君仓皇奔亡关下并伪传亦无之,故欲求一宿终不可得。今以此条律文与《商君传》相参证,情节宛符。可见《史记》所载,确有来历。商君诚所谓“作法自毙”者矣。秦律出土虽仅一小部分,其证史之功用则无穷。不有秦简,今日又乌得知秦廷于游士及私门舍人忌惮之深,防范之严乎?
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
(一)知识分子出现于古代的客观历史条件
在周代封建制度中,“士”本是贵族阶级的最低一层,“士”的上面是“大夫”,下面则是所谓“庶人”了。在森严的封建系统下,社会的流动性极小,“士”的身份因此是相当固定的。另一方面,“士”的封建身份使他有权利也有义务去担任某些实际的职事。金文和其他古代文献告诉我们,古代各种低层官吏如邑宰、府吏、下级军官之类大抵是由“士”来充任的。孔子曾为委吏、乘田,正由于他的封建身份是“士”。所以他自承“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说文解字》训“士”为“事”,顾炎武断定古代的“士”,“大抵皆有职之人”,都是有坚实的根据的。
……
春秋战国之交,随着社会组织的复杂化和官僚制度的成长,政治上的职事一天一天地由简趋繁,这种新的局面必须有大量的“士”才能应付得了,“士”阶层在这一时期的迅速扩大是势所必至的。“士”的地位处于贵族与平民之间,在社会流动十分剧烈的时代,恰成为上下升降的汇聚之所。在封建秩序解体的过程中,这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阶级关系首先在“士”的层面上发生最深刻的裂隙,决不是偶然的。
士庶合流,士阶层扩大,终于使“士”从古代那种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下逮战国,士的地位已从贵族的末席转变为平民的首座,这便是《榖梁传》所指的“士民”(见成公元年条) 。过去的“士”都是“有职之人”,甚至“三月无君则吊”(《孟子·滕文公下》) 。现在则成为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无定主之士便是所谓“游士”了。从社会分工的观点说,“士”在此时已正式被划入“劳心者”的范畴。公父文伯之母在《国语·鲁语》中曾对士、庶之别有如下的描绘:
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
这里所言“讲贯”、“习复”、“计过”各种活动显然都是与知识技能有关的劳心之事。这与庶人以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力”活动截然异途。公父文伯之母既说这一分工理论是“先王之训”,则“士”与“劳心”之间至少在西元前6世纪的初叶已被画上了等号。《左传》襄公九年(西元前563年) 知武子也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后来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那是丝毫不足为异的(参看竹添光鸿《左氏会笺》第十四襄公九年条的笺注) 。
从社会背景来说,“士”从固定的封建身份中获得解放,变成可以自由流动的四民之首,严格意义的知识分子才能出现于古代中国。所以“士”虽然是知识分子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来源,我们却不能把古代文献中所有的“士”都单纯地理解为知识分子,以历史断代而言,中国知识分子之形成一自觉的社会集团是在春秋战国之际才正式开始的。
(二)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的主观条件
上面的分析只是就知识分子最初出现在古代中国的客观历史条件有所说明。但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却另有其更重要的主观方面的凭借,所谓主观凭借不但涉及他们的学术与思想,并且也包括他们的理想与抱负。这些主观条件的构成必须上溯至中国古代的特殊文化传统始能获得比较确切的解释。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色主要表现在礼乐传统上面,也可单以“礼”之一字概括之。孔子说: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所以根据传统的史学观念,礼乐的传统历夏、商、周三代而一脉相承。严格地说,夏代的存在尚待考古发掘的更进一步证实,虽则中国考古学家中已颇有人相信二里头为夏文化之说,但由于最近陕西周原甲骨文的新发现,至少孔子所谓“周因于殷礼”的历史断案已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周人不但继承了殷人的占卜传统,而且周文王也祭祀殷的祖先如成汤及文武帝乙。
礼乐传统至周代而极盛,故孔子又说: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周代贵族子弟大体上都受到礼、乐、射、御、书、数的所谓六艺教育。不用说,其中尤以礼乐两项最为重要,周人当然也不能不依赖武力以巩固其统治,但他们毕竟具有高度的文化教养,在他们的价值系统中,赤裸裸地“以力服人”是最不足取的。因此虽属征战之事也必须“文之以礼乐”,春秋时代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赵衰建议说:
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晋文公便毫不迟疑地接纳了赵衰的意见,“使郤縠将中军”。在同一时代,我们还看到宋襄公“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的例子,那更是在战阵之上讲究礼乐了。宋为殷后,宋襄公的可笑做法如果不是殷商故物,当然就是周代礼乐传统的畸形产品了。封建秩序中的“士”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之下陶冶出来的,《礼记·王制》云: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王制》成篇虽晚,所言亦过于整齐,但颇足以说明“士”的一般文化渊源。持以与上引郤縠“说礼乐而敦诗书”的情况相较,即可见礼乐诗书确是古代贵族(包括“士”在内) 训练的共同基础。
但在春秋战国之前,礼乐是所谓官师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个别的“士”并不能据之为私有的知识技能,也不能各就己见对礼乐传统加以发挥。章学诚所提出的“战国以前无私人著述”的论断便是针对着这种情况而发的。所以从学术思想史的观点言,严格意义的知识分子则是随着王官之学散为诸子百家而产生的。
春秋时代一方面是礼乐传统发展到了最成熟的阶段,另一方面则盛极而衰发生了“礼坏乐崩”的现象。当时的上层贵族有的已不甚熟悉那种日益繁缛的礼乐,有的则僭越而不遵守礼制。无论是属于哪一种情况,礼乐对于他们都已失去了实际的意义而流为虚伪的形式。当时对礼乐有真认识的人则只有向“士”这一阶层中去寻找。“士”在礼乐诗书方面的长期训练使他们自然地成为博文知礼的专家,孔子便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位,所以孔子早在青年时代便以知礼闻名,上层贵族如孟懿子、南宫敬叔都曾向他学礼,而他的弟子之中也有不少是以相礼为职业的人。
这个士的阶层不但娴熟礼乐,而且也掌握了一切有关礼乐的古代典籍。周室东迁以后,典册流布四方,这是王官之学散为诸子百家的一大关键所在。从文化史与思想史的观点说,“士”阶层从封建身份中解放出来而正式成为文化传统的承担者,便正是在这一转变中完成的。孔子以“士”的身份而整理礼、乐、诗、书等经典并传授给他的弟子,尤其是具体地说明了王官之学流散天下的历史过程。关于这一点《庄子·天下》篇有一段总论最值得玩味。《天下》篇说: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天下》篇的作者把王官之学散为百家概括为“道术将为天下裂”一语是极为生动的,后来《淮南子·俶真训》也说: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
此处“列道而议”一语显然是从《天下》篇的“道术将为天下裂”蜕化出来的,这里就直接引出了古代文化史上所谓“突破”的问题。
(三)古代各家的“突破”
所谓“突破”是指某一民族在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通过反省,思想的形态确立了,旧传统也改变了,整个文化终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高的境地。
“哲学的突破”或“超越的突破”是和古代少数圣哲的名字分不开的。中国的孔子、墨子、老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的先知,印度的释迦牟尼都是“突破”的关键人物。但作为古代文化发展中的一个必经阶段而言,“突破”却并不是少数圣哲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相反地,这少数圣哲正由于把握到了文化发展的脉搏才能有所“突破”。所以宋儒所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尚只点明了“突破”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所谓“圣人应运而生”,“运”是指历史上的机运或缘会。必须会合此两面以观,“突破”在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
“突破”的名词虽起于西方近代的学术界,但这个观念则早已出现于中国思想史,前面所引庄子《天下》篇的“道术将为天下裂”一节便是发挥“突破”的观念,“破”与“裂”自然是可以互训的。由此可见,我们用“哲学的突破”或“超越的突破”之说来重释王官之学散为诸子百家这一历史过程,完全没有任何牵强附会的地方。其中唯一新颖之处即“突破”涵蕴了一个比较文化史的观点,不限于古代中国一地而已。从比较文化史的观点出发,西方学者有的认为中国的“突破”表现得“最不激烈”(least radical ) ,有的则说是“最为保守”(most conservative ) 。总之,他们都断定中国的“突破”在古代世界是属于最温和的一型,这一断定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但其所以如此则仍有待于进一步的说明。
一切“突破”都发生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不是凭空而来的:古希腊的“突破”以《荷马史诗》中的神话世界为背景,以色列的“突破”则起于《旧约》所透露的宗教远源。古代中国的“突破”当然也有它的独特的文化基础,那便是上文所说的礼乐传统。前面已经指出,春秋战国是所谓“礼坏乐崩”的时代,王官之学即在此崩坏的情势下散失到士阶层的手中。这一演变,从比较文化史的观点说,也特别值得我们注视。近来讨论“突破”的学者已有人注意到“突破”与“崩坏”(breakdown) 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一般地说,历史上重大的“突破”,往往都有一个“崩坏”的阶段为之先导。 中国古代从“礼坏乐崩”到“列道而议”的历程便恰好为上述的一般观察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天下》篇的作者论“道术将为天下裂”而溯源至“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也正是要点出“突破”与“崩坏”之间的内在联系。古代中国的“崩坏”含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秩序方面的,即前面已讨论的“封建”制度的解体;一是文化秩序方面的,即是所谓“礼坏乐崩”。从思想史的角度说,古代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或“超越的突破”则是起于文化秩序的“崩坏”,换句话说,也就是对于“礼坏乐崩”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反应。儒、墨、道三家的中心理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儒家在诸子百家中兴起最先,因此与礼乐传统的关系也最为密切而直接。这就是《天下》篇所谓“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孔子一生尊重三代相传的礼乐,自称“述而不作”,但另一方面却又极不满当时礼乐之流为僵死的形式而不复有内在的生命。所以他慨叹道: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
孔子的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自未可一言以概其全,但是从基本方向上看,孔子显然是要为礼乐寻求一个新的精神基础: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
礼只是一种象征,它的“本”则深藏在人的内心感应之中,离开了这个“本”,礼便失去其象征的意义了。他又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他终于在这里找到了礼乐的内在根据。礼乐是孔子思想中的传统部分,“仁”则是其创新部分。以发生的历程而言,后者正是突破前者而来。但孔子以“仁”来重新解释礼乐,礼乐的含义遂为之焕然一新,非复三代相传之旧物了。孔子以后,儒家对仁与礼两方面都分别有所发展,孟子的主要贡献偏在仁的方面,荀子则偏在礼的方面。总之,我们可以断言,离开了古代的礼乐传统,儒家中心思想的发生与发展都将是无从索解的。
墨家的“突破”也和古代的礼乐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墨子曾受儒者之业,熟习诗、书、礼、乐(见《淮南子·主术训》及《要略》) 。但是他对礼乐传统的反应却与孔子截然不同。他并不以承继这个传统自许,相反地,他自觉“其道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庄子·天下》篇) 。《墨子》一书中对儒家的攻击,主要也是对礼乐的攻击。所以墨子对礼乐传统的“突破”远比孔子为激烈,但从另一方面看,墨家却又远比儒家为保守。孔子的“仁”是一个全新的观念,是在古代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最大的突破。颜渊问“仁”,孔子说: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子产虽已早倡“天道远,人道迩”之说,但是直到“为仁由己”的观念出现之后,以仁为中心的思想系统才正式建立了起来。墨子则不然。他的“兼爱”论不立足于“人道”,而立足于“天志”,也就是古代的天道思想。故儒、墨两家的中心学说虽同为针对礼乐传统而发,但两者突破的方式却颇不一致。儒家继承了礼乐传统而同时企图从内部改造这个传统,赋予礼乐以崭新的哲学含义——仁;墨家对礼乐持否定的态度,但他们所开辟的新的精神境界——兼爱——则建立在原始宗教的基础之上,这是比礼乐更古老的传统。儒、墨的对照是极其显著的。
最后我们要略谈一谈道家的“突破”。我们所谓道家,基本上是指《老子》和《庄子》这两部书所代表的思想。以我们今天的历史知识而言,这两部道家著作成书颇晚,远在儒、墨出现之后。因此其中所表现的批判锋芒不但针对了礼乐传统,而且还逼向儒家的中心理论。《老子》三十八章云: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此处道德两字是道家的中心观念,仁义则代表儒家的基本理论。以实际的历史进程言,《老子》此章所说可谓适得其反。儒家仁义之说乃突破礼乐传统而出,道家的道德观念则起于仁义之说既兴之后。但是从《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说,文化是自然的堕落,因此这一个发展遂被看成一逐步倒退的过程。《老子》这一段话必须与《庄子·大宗师》篇中论颜回“坐忘”的寓言合参。颜回先忘去仁义的观念,再忘去礼乐的观念,最后且“堕体黜聪,离形去知”,始能达到与“道”合一的最高境界。《庄子》说的是个人“得道”的历程,与《老子》论社会“失道”恰成一往一复。个人要把握住道家之“道”,第一步是超越仁义的观念,第二步是超越礼乐的观念,第三步则是超越随文化而来的一切观念。如此层层上翻,最后便接触到那个“先天地生”的原始道体。荀子虽然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但庄子的“天”与墨子的“天志”不同,它并不乞灵于比礼乐传统更为古老的原始宗教意识。相反地,庄子思想中的“天”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新观念,从道家的观点说,它是比儒家的仁义世界更高一层的领域,所以在《大宗师》篇中,庄子特别假孔子之口提出“游方之内”与“游方之外”的分别,而严格地把儒家划入“游方之内”。
我们对儒、墨、道三家持说的背景略加分疏,便可看到中国古代的“哲学的突破”与“礼坏乐崩”正是一事之两面。上述三家的“突破”方式虽然各异,但脱胎于礼乐传统则并无不同。其余后起诸家也无不或直接或间接地从礼乐传统中发展出来,用刘歆的话说,“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引) 。所以“九流出于王官”和“道术将为天下裂”同样足以说明中国古代“哲学的突破”的特殊性格。诸家的“突破”之间虽有激烈与温和的异趋,但整个地说终不出礼乐传统的笼罩。《天下》篇说墨子“毁古之礼乐”,其实也只限于周末那种过度形式化的繁文缛节,而不是三代礼乐之全部。《淮南子》说: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要略》)
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墨子谓儒者公孟曰:
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墨子·公孟》)
可见墨子不过是要以夏礼来代替周礼而已,道家对文化采否定的态度,故视礼乐为人类堕落的产品。但是他们的“突破”之道是另外开辟一个“方外”的世界,而不去触动那个“方内”的世界。他们深知,文化一经出现便不会自动地消失的了。《老子》有“和其光,同其尘”之论,《天下》篇也说庄子“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这是道家不与“尘俗”决裂的明证。因此尽管道家在批判现实礼乐方面比儒、墨两家表现得都要激烈而彻底,但是在一个更高的思想层次上,他们依然肯定礼乐的意义。像《大宗师》中的孟子反、子琴张两人不肯“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但他们哀友人子桑户之丧,“临尸而歌”,仍自以为得“礼意”。这里我们看到道家“突破”的内在限制。
在诸家的“突破”之中,儒家自然是最温和平正的一支。儒家一方面承继了礼乐传统,整理了古代经典,另一方面又在承继与整理之际将一种新的精神贯注于旧传统之中。这种寓开来于继往的“突破”途径正合乎孔子所谓“周因于殷礼,其所损益可知”那种特殊的变革方式。《诗经·大雅·文王》所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和近代西方学者所说中国史是“在传统中变迁”(Change Within Tradition) 都可以借以说明儒家“突破”的基本性格。儒家之终于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决不是偶然的。韦伯(Max Weber) 曾指出,东方的知识阶层如中国的儒家或印度的婆罗门派往往对流行的官方宗教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或置之不问或在哲学上重新加以解说,但并不断然与之决裂。 以儒、墨、道三家与当时的礼乐传统之间的关系而言,儒家可以说是赋予礼乐以哲学的新解,道家追求一个超越礼乐的境界,但墨家则不免与礼乐发生正面冲突。秦汉以后,儒、道两派各有发展,而墨家一流终于衰竭。其所以如此之故是值得我们细细参究的。
(四)“突破”后知识分子的处境
自“道术将为天下裂”以后,古代礼乐传统辗转流散于士阶层之手,于是知识分子主观方面的构成条件便具备了。孔子说: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孔子这一段话显然是观察古史发展所获得的结论,孔子虽然向往“天下有道”的局面,但他当然更了解他所处的正是一个典型的“天下无道”的时代。以礼乐而论,不但不复出自天子,并且也已不再出自诸侯或大夫。事实上,天下无道则庶人议,自“哲学的突破”以来,礼乐已出自诸子百家了。这便是章学诚所谓“官守失传……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文史通义·原道中》) 。
我们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哲学的突破”以前,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借可恃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已发展了这种精神凭借,即所谓“道”。孔子曾毫不迟疑地指出“士”是“道”的承担者: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
他的弟子曾参更把对“士”的道德要求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孔门师弟用“突破”以后的眼光来重新为“士”下定义,最可以使我们看出士阶层所发生的变化之大。此时“士”的特性已显然不在其客观的社会身份,而在其以“道”自任的精神。《说文解字》“士,事也”的定义仅适用于“封建”秩序下各有固定职事的“士”,但已不足以尽“突破”后的新士的底蕴。“士”在社会性格方面所发生的基本变化最可以从孟子下面这一段对话中窥见: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
王子垫需要问“士何事”,这就显示“士”的功能已与前大异,而且新的士风尚在形成之中。孟子答语则是发挥孔子“士志于道”之说,因为仁义恰是儒家之“道”的主要内涵。由此可见“突破”以后的士不但已摆脱了“封建”身份的羁绊,并且其心灵也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他们已能够超越个人的工作岗位(职事) 和生活条件的限制而以整个文化秩序为关怀的对象了。所以孟子又说: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
现代社会学家曾指出: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阶级,因此他才能坚持其“思想上的信念”(intellectual convictions) 。而一般人则往往跳不出个人的阶级背景的限定。这个说法正是孟子“恒心”论的现代翻版。孔子所谓“士而怀居”或“耻恶衣恶食”便不足为“士”,也是指着这种知识分子的情操而言的。所以刘向《说苑》重新给“士”下定义云:
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卷十九《修文》)
这才抓住了“突破”以后的“士”的基本特征,也就是现代人所称的知识分子了。当然,孔、孟以至刘向关于“士”的界说都只能当作“理想典型”(ideal type) 来看待。事实上真能合乎这种标准的士终属少数。但是从诸子百家竞起,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情形来看,这些少数的士无疑在当时的历史潮流中是处于主导的地位的,他们正是汤因比(Arnold Toynbee) 所谓的“创造少数”(creative minority) 。
春秋战国之际,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出现以后,首先便面临着如何对待政治权威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涉到两个方面:从各国君主一方面说,他们在“礼坏乐崩”的局面之下需要有一套渊源于礼乐传统的意识形态来加强权力的合法基础。从知识分子一方面说,道统与政统已分,而他们正是道的承担者,因此握有比政治领袖更高的权威——道的权威。《淮南子·修务训》云: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
这段话虽是从批判的角度出发,却恰好把两面的情况都说明了。但是必须指出,道统与政统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也有紧张和冲突的一面,这不仅古代中国为然,其他经验了“哲学的突破”的古文化都遭遇过同样的问题。以色列的先知、伊斯兰的教长(Clama) ,以及基督教的教宗无不与世俗的王权之间发生过程度不等的摩擦。不过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不同,“突破”并没有带来天上王国与人间王国的清楚分野,耶稣与恺撒之间也始终无法划明权责。故中国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是别具一格的。
中国的道统包含了宗教的成分,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谓的宗教,它不具备有形式的组织。以“官师治教分”(章学诚语) 的情况而言,它和西方文化中政教分立的状态未尝没有可以比拟之处。然而西方“国家”(state) 与“教会”(church) 对峙的局面则从来不曾在中国史上出现过。(佛教传入之后,沙门不致敬王者尚不能为东晋南朝的帝王所容,其他更不用说了。) 不但如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从“封建”秩序中的“士”阶层蜕化出来的,他们也不能像西方专司神职的教士那样不理俗务。在这种情形下,道统与政统之间要想维持一种微妙的均衡便十分困难,一切都只有靠个人的判断了。孟子说:
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尽心上》)
孟子在这里正式提出了“道”与“势”(即政统) 的关系的问题,而且很明显地是把“道”放在“势”之上,但是他对于怎样使道与势的关系达到一种恰如其分的境地却没有具体的说明,因此唯有期之“贤王”与“贤士”双方的自觉努力。
依照当时的一般观念,士和君主的关系可分为三类,即师、友与臣。《孟子》引费惠公之言曰:
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万章下》)
足为明证。又《战国策》记郭隗答燕昭王语云:
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燕策》)
郭隗所说的是君主择士的标准。除最后一类可以不论外,师、友、臣三项正与《孟子》若合符节。大概当时君主对少数知识分子的前辈领袖是以师礼事之,其次平辈而声誉卓著的以友处之,至于一般有学问知识的人则用之为臣。这种分别在战国史上是到处可以得到印证的。
……
现在我们要追问,何以在君主与知识分子之间会发生这种师、友、臣的等级划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道”需要具备某种架构以与“势”相抗衡。道统是没有组织的,“道”的尊严完全要靠它的承担者——士——本身来彰显。因此,士是否能以道自任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他和政统的代表者——君主——之间是否能保持一种适当的个人关系。首先,我们都知道,在理论上,知识分子与君主之间的结合只能建立在“道”的共同基础上面。所以孔子说: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
孟子也说: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
……
政统与道统显然成为两个相涉而又分立的系统。以政统言,王侯是主体;以道统言,则师儒是主体。后来“德”与“位”相待而成的观念即由此而起。孟子说得最清楚:
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孟子·万章下》)
但若真要使“天下有道”,“德”与“位”则必须互相配合,不可或缺。所以《中庸》说:
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为了使“德”与“位”旗鼓相当,知识分子便不能不“自高”、“自贵”以尊显其“道”,即所谓“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也(《孔丛子·居卫》篇) 。
……
《史记》明言孟子“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孟子荀卿列传》) 。虽不用其道而仍欲尊其人,这正是因为齐宣公深切地了解到“道”在政治上自有其无比的号召力。但最能够说明其时“道”与“势”的关系者则无过于齐国稷下学之兴起。《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稷下学有两个特点最值得注意:第一是君主待知识界领袖以师友之礼;第二是这些知识界领袖的专职即是各持其道以批评政事。
上引《史记》文中“上大夫”是“列大夫”之误(见《孟子荀卿列传》) 。“列”是“比”义,即比爵大夫。换句话说,这些稷下先生并不是齐王廷的臣僚。所以田骈虽名列稷下,受政府奉养,但仍然自居为“不宦”(见《战国策·齐策》) 。“先生”也是齐王对他们的一种尊称,表示以师礼相待之意。齐襄王时荀卿在稷下号称“最为老师”即可为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语) 。稷下先生不但在齐国特受崇敬,其他各国君主也多争以师礼事之。最著名的如驺衍,据《史记》所载:
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孟子荀卿列传》)
稷下、碣石这一类学宫的建立是魏文侯、鲁缪公礼贤以来“道”、“势”关系的形式化与制度化,其历史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稷下先生的“不治而议论”也足以说明“道”、“势”关系的新发展。“不治”表示他们“无官守”,即不在官僚系统之内,易言之,即不是君主的臣下而是“师”或“友”。“议论”则是今天所谓的批评。《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之“论”、《论语》“庶人不议”及《孟子·滕文公下》“处士横议”之“议”,都是很明显的例证。“士”有议论的传统自周代已然,所以《左传》襄公十四年有“士传言”之语。但是把知识分子和批评完全等同起来,并由官方正式加以承认,则始自稷下。更重要的,这些知识分子都是以自己所持之“道”来批评时政的,因此《淮南子》才说儒、墨“裂道而议”。另一方面,刘向《新序》说“稷下先生喜议政事”(《杂志第二》) ,《盐铁论》则说他们“不任职而论国事”(《论儒》) 。这便证明稷下先生的批评确是专以“政事”、“国事”为对象的。我们知道西元前4世纪以来各国君主都争用纵横法术之士以求富国强兵。这当然也是知识分子获得普遍重视的一大原因,但是这个原因却完全不能用来解释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的盛况。这些稷下先生既“不任职”,自不可能在富国强兵方面发生任何直接的作用。事实上,他们都是因为号称代表了某种“道”才受到君主的师礼待遇的。孟子言必仁义固不待言,其余我们所知的稷下先生如彭蒙、宋钘、尹文、慎到、田骈等也都是各学派的宗师。他们正是《庄子·天下》篇和《淮南子·俶真训》所说的“裂道而议”的人物。晚期的稷下先生如荀卿、驺衍也依然是以“道”起家的。以驺衍而论,他观阴阳消息,论五德终始,提倡一种新的“天道”。因此当时有“谈天衍”之号。这种“道”显然与富强无关。从比较宗教学的观点看,战国君主的“尊师重道”主要只说明一个问题,即政统需要道统的支持,以证明它不是单纯地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更重要地,在西元前4世纪至西元前3世纪这个历史阶段中,几个主要国家如齐、秦、魏(梁) 、赵、燕等都有统一天下的雄图。它们当然更需要在武力之外另发展一套精神的力量了。梁襄王和孟子关于“天下恶乎定”(《孟子·梁惠王上》) 的一番讨论便透露出此中的消息。但由于当时的政统和道统都没有“定于一”,所以不但各国君主争礼不同学派的领袖,而诸子百家也莫不竞售其“道”以期获得“正统”的地位。
司马谈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是一句很有根据的论断,必须从当时“道”与“势”之间的微妙关系中去了解。儒、墨、道、法四家直接系乎治道,固不待论,名家与阴阳家则代表早期逻辑与宇宙论方面的思想,何以也与治道有关?荀子明明批评名家“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荀子·非十二子》) ,司马迁也说阴阳家“闳大不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今此二家著述多散佚,我们已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则是他们确都曾努力把自己的“道”和“治天下”联系起来。所以驺衍的学说“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公孙龙自称“少学先生之道,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庄子·秋水》篇引) 。刘向《别录》也记名家“论坚白异同,以为可以治天下”(《汉书·艺文志》注引) 。无论名家与阴阳家是否真有助于“治天下”,他们如此宣说却透露出当时知识界的一种动态,即“道”的一方面也同样有迁就“势”、配合“势”的情况。孟子坚持不应“枉道而从彼‘势’”(《孟子·滕文公下》) ,便是针对这种历史背景而发的。
(五)结语
上文对“哲学的突破”以后知识分子在“道”、“势”之间之处境作了一番初步的分析。从这个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若干基本特征都已在此时露其端倪。第一,在理论上,知识分子的主要构成条件已不在其属于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如“封建”秩序下的“士”,而在其所代表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其根据即在于此。第二,中国的“道”源于古代的礼乐传统,这基本上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其中虽然也含有宗教的意义,但它与其他古代民族的宗教性的“道统”截然不同。因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恺撒的事,后世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观念都是从这里滥觞出来的。第三,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所以根据“道”的标准来批评政治、社会从此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内之事。由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的事观之,知识分子这种“言责”早在西元前4世纪时即已为官方所承认。第四,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此外便别无可靠的保证。中国知识分子自始即注重个人的内心修养,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他们不但在出处辞受之际丝毫轻忽不得,即使向当政者建言也必须掌握住一定的分寸。清初黄宗羲送万季野北行诗:“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便是这个传统的实际表现。
以上是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当作一种典型(ideal type) 来观察而获得的四点概括。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征当然不尽于此,不过这几点确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但是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的目的不是要美化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形象,更不是说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知识分子都合乎这种典型。事实上,正由于中国的“道”缺乏有形的约束力,一切都要靠个人的自觉努力,因此即使在高级知识分子群中也有许多人守不住“道”的基本防线。孟子已斥公孙衍、张仪为“以顺为正,妾妇之道”(《孟子·滕文公上》) 。荀子更对当时许多“仕士”和“处士”的丑行毫不保留地予以暴露(《荀子·非十二子》) 。至于散在贵族私门的那些大量的“食客”,自然越发经不起典型标准的衡量了。但是现代史学家的任务也同样不是谴责历史上的人物,最重要的是怎样去说明这种历史现象。因此我们便必须回到社会史的领域去寻找线索。
古代知识分子从“封建”身份中解放出来之后,虽然在精神上能驰骋于自由的王国,在现实生活上却反而失去了基本的保障,不像以前的“士”大体上都是“有职之人”,极少有失位之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号称“游士”固与周游列国有关,但也未尝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固定的经济基础之故。苏家的人对苏秦说:
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史记·苏秦列传》)
此时知识分子已成为“四民之首”。其余三民都各有本业,唯独“士”的凭借是他的知识和技能,不能不靠“口舌”来谋生。这在当时知识分子大量涌现而竞争激烈的时代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李斯将西入秦游说,辞其师荀卿曰:
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的话其实说得很沉痛,足以说明一般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从社会来源说,战国知识分子不出没落贵族和下层庶民两大范畴,但他们几乎都已贫穷到“无以为衣食”的境地。历史上的例子很多,都可为李斯的话作注脚。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保持以道自重的节操是不可能的。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事实上只能期之于极少数突出之“士”,因此但有“典型”的意义,而无普遍的意义。这不仅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然,古今中外亦莫不皆然。不过在中国的“道”缺乏形式约束的特殊状态之下,“枉道而从势”或“曲学以阿世”更为方便罢了。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们必须稍稍讨论一下秦汉统一在“道”与“势”的关系方面所发生的影响。如上面所指陈,先秦时期的一般知识分子,都游于各国王侯之门,上者猎取卿相,下者亦可获得衣食,而知识界领袖如稷下先生之流则更受到君主的特殊礼遇。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则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即列国间的激烈竞争。在争霸的迫切要求下,各国君主不但需要种种知识与技能,而且更需要“道”的支持。及至秦汉统一,政治形势为之大变,四方游走的知识分子显然成为一股离心的社会力量,而不利于统一。大一统的政权也同样不能容忍众“道”纷然杂陈的局面,因为众论纷纭不免破坏人民对统一的政治权威在精神上的向心力。所以秦国在霸局既定之后即下“逐客”之令,要把来自各地的游士都驱逐出境,而统一天下之后则更进一步要以“势”来统一“道”。李斯请禁私学的奏议说:
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史记·李斯列传》)
这一篇奏议古今熟诵,但是很少人了解它是系于先秦以来“道”、“势”消长的关键性的文字。法家不师古,历史文化传统对他们而言是没有真实意义的,故他们即以今王之“法教”为“道”之所在,换句话说“道”是从“势”中派生出来的。奏文中所言“道古以害今”、“各以其私学议之”,都是指秦廷博士而言的。博士虽起于六国之末,但其详已不可考。我们所知的博士制度则是秦代所创建而汉人因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博士”条本注云:
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百官》二)
“掌承问对”即是稷下先生的“不治而议论”,所以“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可见博士仍继承了先秦知识分子批评政治的传统,《水经注》“淄水”条注云:
汉以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史记音义》曰:“欲以继踪齐稷下之风矣。”(《永乐大典》本卷十一)
可见博士与稷下先生确有制度史上的渊源,但以政治功能而论,二者却大不相同:稷下先生“不治”、“不宦”,俨然与君主为师友;博士则已正式成为臣僚,不复能恃“道”与帝王的“势”抗礼了。尽管如此,博士承自稷下的议政之风,仍不能见容于大一统的政权,“势”长“道”消的情形于此可见一端。汉代自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孔子之“道”至少在表面上已成为正统。这可以说是汉比秦高明之处。但是和先秦时代相较,“道”在汉代的地位则已远不足与“势”相颉颃。班固《典引》云:
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俾其承三季之荒末。……故先命玄圣,使缀学立制。宏亮洪业,表相祖宗。……虽皋、夔、衡、旦,密勿之辅,比兹褊矣!(《文选》卷四十八)
这里的“玄圣”“立制”自是指孔子为汉立法那一套说法而言,但孔子的地位仅相当于皋、夔、衡、旦之类的帝王辅弼,是汉臣而不是帝师。这与先秦儒者谓“夫子贤于尧、舜”(《孟子·公孙丑上》) 或“孔子当圣王”、“为天子”(《墨子·公孟》) ,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了。清代的雍正说:“使孔、孟当日得位行道,惟自尽其臣子之常经,岂有韦布儒生要自做皇帝之理?”(《大义觉迷录》卷二) 从汉到清,政统给道统所正式规定的位置大体上就是如此,虽则这种片面的定位并未获得道统方面的承认。
大一统的“势”既不肯自屈于“道”,当然也不能容忍知识分子的气焰过分高涨。所以随着秦汉统一帝国的建立,游士的时代便进入了结束的阶段。最近出土的“云梦秦简”中有“游士律”一项是有关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新史料。现在我们已确知在秦代统一的前夕,秦国不但对外来的游士严加控制,而且也严禁本国的知识分子外游。商鞅教秦孝公“禁游宦之民”(《韩非子·和氏》) 的法令竟完全获得了证实。汉初因采用了部分的“封建”制,游士曾一度恢复了他们旧日的活跃。但汉代也同样不能允许知识分子无限度地自由流动,武帝元朔二年(西元前128年) 下“推恩诏”削藩以后,游士终与诸独立王国同归于尽。桑弘羊说得最明白:
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谋叛逆,诛及宗族。(《盐铁论·晁错》)
从此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游士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兼论“俳优”与“修身”
近几十年来,西方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家和史学家,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兴趣甚为浓厚,意见尤其分歧。大体上说,我们可以分辨出两种看法:早期的讨论比较强调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格,即知识分子因为不成其为一固定的社会阶级或团体,而发展出一种自由批判的精神。最近十余年来,关于西方知识分子的讨论渐渐转移到历史的渊源方面,因此有的人强调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传统”问题。这就与宗教发生了直接联系。从这个观点说,知识分子批评现实,主要是因为现实不合于他们所维护的一些基本价值。古代的基督教既代表一种价值系统,当然也成为社会批判的根据了。照这种说法,知识分子的后面总是有一个“神圣的”(Sacred) 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虽已与中古的宗教分离了,但就其所关切者是最终极的价值而言,他们仍可以说是代表了一种“神圣的”传统。据前一种看法,知识分子主要是以自由人的身份来批判一切的;据后一种看法,则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来自他们所代表的神圣传统——相当于中国所谓的“道”。
西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一时还不可能获得完全一致的结论,甚至如何给知识分子下定义,也不免家异其说。以上两种看法其实只是着眼点的不同,并不必然互不相容。但由此可见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想把知识分子截然划分为传统型与现代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再进而论中西知识分子型态的异同,其困难自然更多。不可否认,中国知识分子自有其特殊的性格,但是这种特殊性基本上是来自中国文化的传统。若仅以型态而论,则中西知识分子之间也未尝没有大体相同之处。例如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在社会身份和思想上都以“自由流动”显其特色,我们在战国所谓“游士”的身上也找得出这种痕迹。但中国古代的“士”又多以“道”自任,这就近乎西方古代和中古的宗教型的知识分子了。而且型态之近似并不能掩其实质之殊异,这尤其是喜欢比较中西文化异同的人所不可不注意的事。本文正是企图从异同之际着眼,讨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某些特色。
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虽没有获得一致的定义,但他们都肯定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性格,即以批评政治社会为职志。这在中国也不例外。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反过来说便是“天下无道,则庶人议”。而天下永远是处在“无道”或不尽合于“道”的状态。这里的“庶人”也包括“士”。“议”即是“批评”。故孟子有“处士横议”之语。西方学者中强调知识分子是自由人的一派往往不肯溯其源至宗教的传统,他们转而求之于俗世的背景。德国的社会学家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 因此把中古宫廷中的“俳优”(Fools) 看成现代知识分子的前身。“俳优”在社会上没有固定的位份,他们上不属于统治阶级,下不属于被统治阶级;既在社会秩序之内,又复能置身其外。所以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用插科打诨的方式说真话,讥刺君主。西方的“Fools”另有“愚人”的含义,也就是说真话的傻子。这一“愚”的美德在西方思想史上备受赞扬。最著名的作品自然要数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的《赞愚》(The Praise of Foly) 了。这种“愚”并不是老子所谓“大智若愚”或颜回的“不违如愚”,而近乎宁武子的“其愚不可及”之“愚”。不过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并没有把“愚”和“俳优”直接联系起来,更没有想到用“俳优”来和“士”相提并论。
但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也不是与“俳优”毫无渊源。司马迁《报任安书》说得很明白: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可见在帝王心目中,像司马迁这样的文史专家也不过和倡优差不多,可以加以戏弄的。司马迁之所以特立《滑稽列传》正由其深有身世之感。因为《滑稽列传》中不但包括了俳优如优孟、优旃之流,并且也包括了俳优型的知识分子如淳于髡。淳于髡名列齐国的稷下先生,是一位声望很高的知识界领袖。《史记》又说他“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尤以“谏说”著称(见《孟子荀卿列传》) 。汉武帝时的东方朔也和他是同一型的人物。淳于髡、东方朔和俳优的共同之点便是“言谈微中,亦可以解纷”。他们都能寓严肃的批评于嬉笑怒骂之中,“滑稽”一词即取义于此。
西方俳优有讥刺的自由,不致受到惩罚。中国亦复如此。晋国的优施曾说:“我优也,言无邮。”(《国语·晋语二》) “邮”是“尤”的假借字,意思是说俳优无论说什么话都是没有罪的。不但优言无罪,甚至优行亦得免罪,五代时名优敬新磨手批后唐庄宗(李存勖) 之颊而竟仍能以巧语自解(见《新五代史·伶官传》及《资治通鉴·后唐纪一》) 。中国历史上俳优巧妙地指斥帝王与权贵的故事可说从来没有中断过。北宋的童贯、南宋的史弥远,在他们权势熏天之际,便正是优伶讥骂的对象。周密说优人“巧发微中,有足称言者”(见《齐东野语·优语》条) ,是完全不错的。可见“言谈微中”的滑稽传统在中国戏台上一直没有断过。清末、民初,皮黄演员借题发挥,嘲弄政治人物的故事还在大量地流传着。
俳优的滑稽传统对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有影响。东方朔的诙谐当时人便已说他“口谐倡辩”、“应谐似优”了(《汉书》本传“赞”) 。同时代的枚皋以辞赋著称,更是有意识地模仿俳优,自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汉书·枚乘传》附) 。唐代王琚则自称:“谈谐嘲咏,堪与优人比肩”(《旧唐书》本传) 。这些事实都可以为司马迁“文史星历……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的话作注解。后世如苏东坡“一肚皮不合时宜”,因此“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多少也与俳优传统有关。元好问论诗绝句“俳谐怒骂岂时宜”即明为东坡而发。以“俳谐”易“嬉笑”,足见遗山听曲识真,绝不仅是为了平仄之故。不过知识分子究竟不是俳优,得不到“优言无邮”的待遇,而中国又不比西方,知识分子可以在“愚”的传统里免祸全身。所以用“俳谐怒骂”的方式说老实话的人,只有以“狂”自居。传说中的箕子向纣王进谏不从,而披发佯狂,这才降为奴隶,免除一死。孔子说:“古之狂也肆。”(《论语·阳货》) 便是指着箕子型的肆意直言而说的。东方朔不就是被人呼为“狂人”吗?(《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补传》) 中国史上特别有“狂士”一型人物,大抵都和说老实话有关系。广武君引秦汉之际的成语,即有“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史记·淮阴侯列传》) 。可见其时已以“狂”与直言为不可分,此语唐代魏徵也引之以谏太宗(《资治通鉴·唐纪十》,贞观八年条) 。严光答司徒侯霸语:“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汉光武也笑他是“狂奴故态”(《后汉书·逸民列传》) 。严光披羊裘垂钓,又以足加光武腹上。这些都是佯狂的表演。唐初谏议大夫王珪直言无隐,仍自称是“罄其狂瞽”(《贞观政要·求谏》) 。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狂”的传统真足与西方的“愚”交相映发。尤可注意者,二者都与俳优有相当程度的内在关联。“狂”与“优”有一个基本相同之点,即不以真面目示人。优孟衣冠固然是扮演非我的角色,佯狂也同样非复原来的自己了。事实上,也只有在这种假扮的情况下,说老实话的人才能为“人主”所优容。所以“优容”、“优假”之“优”字断然是与“俳优”之“优”有语源关系的。
上面所说的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侧影之一面。这一侧面恰巧与西方传统有类似的地方。但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却是十分庄严的,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士”或“士大夫”。从正面来看,中国知识分子来自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源头。从孔子开始,知识分子就以“道”自任,而这个“道”则是中国所特有的。先秦初起的三大学派——儒、墨、道——尽管各道其所道,但他们在代表“道”说话这一点上却并无例外。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仅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不同,而且与近代以前西方的“道”的代理人也大有区别。
……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直接承三代礼乐的传统而起。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礼乐已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诸侯,故孔子斥之为“天下无道”。统治阶级既不能承担“道”,“道”的担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礼义”的“士”的身上。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史上最先出现的一位知识分子。中国古代当然早已有了知书识礼的“士”,今天所发现的甲骨文的卜人(或称“贞人”) 无疑便是有知识的人。但是孔子以前的“士”只是古代贵族社会中的一个固定阶层,他们不曾超越位份的限制而自由地思想,更没有资格以“道”自任,因此还不具备今天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的条件。前引司马迁“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那一段话正可为古代不少知书识礼的人的写照。孔子以后,士的处境开始有剧烈的变化。孔子首先便对“士”重新加以界说。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又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 这种新的“士”才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士”成为“道”的承担者是经过一段曲折的历史发展的,此处不能详论。简单地说,这一发展包括了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因素。客观方面是“士”从古代“封建”秩序中游离了出来,获得身份的解放;主观方面是“礼坏乐崩”、王官失守之后,诗书礼乐的传统流散到“士”阶层之手。古代的“士”本来就熟习礼乐,接近典册,孔子本人成学的经过便是显证。所以这个发展是顺理成章的。
古代的礼乐虽具有宗教性(“天道”) 的成分,但这个传统到了孔子手中却并没有走上“天道”的方向而转入了“人道”的领域。这种发展的方向当然不是孔子个人所单独决定的,春秋以来,中国文化已日益明显地有从天道转到人道的倾向。西元前523年郑国的子产即已明白地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的见解。孔子以后,百家竞起,虽所持之“道”不同,但大体言之不但都与诗书礼乐的传统有渊源,而且也都以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为最后的归宿之地。因此刘歆说诸子“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司马谈则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两家的论断恰好是一原其始,一要其终。(这里面当然涉及非常复杂的思想史上的问题,详细分析与论证见本书《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和《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两文。)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自始即受到他们所承继的文化传统的规定,就他们要管恺撒的事这一点来说,他们接近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但是就他们代表“道”而言,则他们又接近西方中古的僧侣和神学家。由此可见以西方的标准来分别知识分子的传统性格与近代性格,施之于中国的情况终不免进退失据。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持的“道”是人间的性格,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
……
前面已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不但自始即面对着巨大的政治权势,而且还要直接过问恺撒的事。他们虽自任以“道”,但这个“道”却是无形的,除了他们个人的人格之外,“道”是没有其他保证的。以孤独而微不足道的个人面对着巨大而有组织的权势,孟子所担心的“枉道以从势”(《滕文公下》) 的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而且事实上也常常发生,汉代公孙弘的“曲学阿世”便是最著名的例子。为了使“道”不受委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进行了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努力。客观方面他们要建立“道”尊于“势”的观念,使拥有政治权势的人也不能不在“道”的面前低头。因此孟子有道尊于势之论,荀子以圣与王并列,“圣者尽伦,王者尽制”,《中庸》也德、位双提。他们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多少发生了一些效果,虽然并不能彻底地驯服“势”,至少后世的知识分子之中颇不乏接受这种观念的人。明末的吕坤说得最痛快直截:
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呻吟语全集》卷一之四)
可见这个传统从战国到明末始终保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在主观方面,古代知识分子则提倡内心修养,这是要给“道”建立内在的保证。关于这一方面,我在有关知识分子的旧作中仅引而未发,现在不妨借这个机会略加补充。在西方和其他文化中,只有出世的宗教家才讲究修养,一般俗世的知识分子似是很少特别注意及此的。中国知识分子入世而重精神修养是一个极显著的文化特色。中国何以有此文化特色是一个极难解答的问题,也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我在这里只想从历史发展的观点上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之强调修养不但与“道”的性格有关,并且涉及“道”与“势”之间的关系。
在“礼坏乐崩”之余,人间性格的“道”是以重建政治社会秩序为其最主要的任务。但是“道”的存在并不能通过具体的、客观的形式来掌握。
……
《论语》中有一段孔子关于君子修身的话最值得注意: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孔子最初是把“修己以敬”作为一种普遍命题而提出的。但子路不以此为满足,层层逼问“修己”到底有何目的和效用,所以最后孔子只好说明“修己”始能“安人”、“安百姓”。可见“修身”的观念并非凭空而起的,而是以建立政治社会秩序中之“道”为其终极的目的。这样已明显地透出所谓“德治”的意思,所以孔子特别举尧、舜为例证。后来孟子对这一方面发挥得更为透彻。但是“修己”在孔子只是“安百姓”的必需条件,而不是充足条件,因此他才说虽尧、舜也未必能完全做得到这一点。通观全段文字,孔子“修己”之说毫无疑问是针对着知识分子而提出的。不过由于人君在政治社会秩序中是处于枢纽的地位,他当然更应有“修己”的必要。政治中心无“德”而能达到“天下有理”的境界是不可想像的。后世儒家特别强调皇帝必须“正心诚意”,其故即在于是。朱子一生对皇帝便只说“正心诚意”四个字。不但如此,“道”的重任虽在“士”的身上,而“道”的实现则是社会上人人分内之事。在这个意义上,“修己”是一个普遍性的价值。荀子论“君道”一再说“闻修身,未尝闻为国”。又说:“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均见《荀子·君道篇》) 稍后《大学》所谓“自天下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正是从荀子思想中演变出来的。
“修身”之为内在道德实践虽最早由孔子正式提出,但它并不是儒家的专利品。事实上,最先用这两个字为篇名的是墨子。(孔子言“修己”,义则一致。当时各家皆言修身,故近人疑《墨子》此篇为伪作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老子》第五十四章有“修之于身,其德乃真”的说法。《管子》一书中原来也有《修身》一篇,可惜早已遗失了。荀子的《修身篇》反而最后出。可见这是古代知识分子共有的观念。墨子论修身有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他开宗明义即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则他讲“修身”是专为知识分子而发的。第二,篇中数见“……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至少在字面上很接近孟子的“反身而诚”。第三,他论及“修身”的弊病,其中有一项便是“守道不笃”,尤可证他相信“修身”足以坚定知识分子对于“道”的信持。在墨子的时代,“士”与“势”的关系已十分密切,常常面临出处辞受的问题。墨子是主张出仕当以“义”为根据的人,因此“修身”便更为迫切不可缓了。他说:
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愠。是犹欲其墙之成,而人助之筑则愠也,岂不悖哉!(《墨子·贵义》)
“修身”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处境息息相关,这在墨子思想中已表现得很清楚了。
后世儒家修身最推重孟子,《孟子·公孙丑上》篇中的所谓“知言养气”章和《尽心》上下两篇,尤为古今儒家聚讼之所在。我们稍一检讨其中所透露的有关精神修养的效用方面,即可知孟子之强调修身,尤其和他之特别重视知识分子的出处辞受有不可分的关系。“知言养气”章说: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
以下即论北宫黝、孟施舍之养勇,并旁及子夏之笃信和曾子之反求诸己云云。由此可见孟子的修养正是使他能对权势“不动心”的根据。此处论“养”专引古代勇士为证,则这种功夫大约与武的传统有特殊渊源。但至孟子之世已为知识分子所普遍地借用了。精神修养不限于儒家,这一章也提供了最可靠的证据。告子“不动心”先于孟子,当然也是修养的结果。
……
以上论中国知识分子注重修身的特色,旨在发掘其历史的背景。总之,一方面中国的“道”以人间秩序为中心,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另一方面,“道”又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弘道”的担子完全落到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一条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作“道”的保证。所以《中庸》说“修身则道立”。儒家因此而发现了一个独立自足的道德天地,固是事实。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儒家的最初与最后的向往都是在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上面。不但《大学》的修、齐、治、平明确地揭示了儒学的方向,《中庸》也同样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我不否认心性之学在宋明思想史上的中心意义,但“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论语·公冶长》) ,原始儒家至少是不甘心如此退藏于密的。朱子重订“四书”而必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朱子语类》卷十四) ,又说“平生精力全在此书”(《朱子语类》卷十四) ,这些话都值得我们深思。不但如此,前已指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重修身者并不止儒家一家,《墨子》与《管子》书中都有专篇讨论。这个重要的事实,如果不从当时知识分子的处境以及“道”与“势”的关系多方面去着眼,则将无从索解了。
中国知识分子虽然自始便有重视“修身”的传统,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肯定他们人人都在精神修养上有了真实的造诣。事实上,在战国中晚期“修身”不但已成为“士”的标记,而且世主也以此为取“士”的标准。“修身”既入于利禄之途就必然不免要流为虚伪。《淮南子·主术训》篇末云:
士处卑隐,欲上达必先反诸己。上达有道,名誉不起而不能上达矣。取誉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誉。信于友有道,事亲不说,不信于友。说亲有道,修身不诚,不能事亲矣。诚身有道,心不专一,不能专诚。道在易而求之难,验在近而求之远,故弗得也。
这段话已明白显示修身是取誉的手段,取得名誉之后,“士”才有上达的机会。《淮南子》成书已在正心诚意说流行之世,因此文中归宿于“心专始能诚”。从“修身”转至正心、诚意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可以说明知识分子向自身寻求“道”的保证之不易。荀子深斥当时处士“心无足而佯无欲”,“行伪险秽而强高言谨悫”(《非十二子篇》) 。足证“修身”早已流于虚伪了。所以战国晚期讲“修身”的人愈转愈内向,《大学》所言“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即是这一内向发展的高峰。不但儒家如此,其他学派的修养论也有同样的倾向。《管子·心术下》说:“心之中又有心,意以先言,言然后形,形然后思,思然后知。”姑不论这两家的功夫论有何异同与交涉,其同为层层向内则是完全一致的。总之,由于“道”没有外在的、客观的保证,知识分子不得不走“修身以立道”的内倾路线,最后终于归宿到“心之中又有心”上去了。
先秦时代,列国竞争,“势”对于“道”多少还肯牵就。大一统政权建立之后,“势”与“道”在客观条件上更不能相提并论,知识分子的处境因此也更为困难。他们除了内向以外,有时也不得不向外寻找“道”的客观基础。董仲舒抬出一个“天”字显然有镇压“势”的作用,而程、朱一派把心性主体贯通到客体性的“理”,多少也含有与“势”抗衡的意味,前引吕坤的话便是明证。但大体而言,中国知识分子终是在“内圣”方面显其特色的。
无论是“俳优”型或“以道自任”型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都有正负两面的表现。以负面言,韩非早就指出:“优笑侏儒,左右近习,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韩非子·八奸》) 后世宫廷中文学侍从之臣自不乏“唯唯诺诺”之辈。讲心性之学也同样不是“道”的必然保证。宋、明以来,“其书则经,其人则纬”(全祖望论李光地语) 的伪道学更是指不胜屈。但是从正面看,“言谈微中”的狂优和持“道”不屈的君子,即使在中国史上最黑暗的阶段也未尝完全绝迹。正是因为这些人物的前仆后继,中国今天才依然存在着一个不绝如缕的知识分子的传统。
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
(一)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
本文的主题是阐释汉代的循吏在中国文化的传布方面所发挥的功用。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对本文的研究取向略加说明。
近几十年来,许多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不再把文化看作一个笼统的研究对象。相反地,他们大致倾向于一种二分法,认为文化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他们用各种不同的名词来表示这一分别:在50年代以后,人类学家雷德斐(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之说曾经风行一时,至今尚未完全消失。 不过在最近的西方史学界,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与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观念已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名词尽管不同,实质的分别却不甚大。大体来说,大传统或精英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级的,而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则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由于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根据的经验都是农村社会,这两种传统或文化也隐含着城市与乡村之分。大传统的成长和发展必须靠学校和寺庙,因此比较集中于城市地区;小传统以农民为主体,基本上是在农村中传衍的。
以上所描述的当然只是一个粗略的轮廓,如果仔细分析起来,则无论是大传统或小传统都包括着许多复杂的成分。通俗文化的内容尤其不简单,可以更进一步分成好几个层次。例如欧洲中古以来的通俗文化中便有所谓“俗文学”(chap-book)一个层次,相当于中国的“说唱文学”。主持这种俗文学的人也受过一点教育,不过程度不高,不能精通拉丁文而已。所以有的史学家甚至把这种“俗文学”看作大、小传统之间的另一文化层。 但是大体而言,上述的二分法还是为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概念架构。
本文讨论中国文化也接受大、小传统分化的前提,而着重点则和时下一般的研究稍有不同。西方目前的潮流是以通俗文化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者虽然也注意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但他们的重心显然在后者而不在前者。 本文的研究对象则是中国的大传统及其对通俗文化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是存心立异,而是受到中国的特殊的历史经验所限,不得不如此。
中国文化很早出现了“雅”和“俗”的两个层次,恰好相当于上述的大、小传统或两种文化的分野,《论语·述而》: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雅”与“夏”音近而互通,故“雅言”原指西周王畿的语音,经过士大夫加以标准化之后,成为当时的“国语”。但是标准化同时也就是“文雅化”,因此到了孔子的时代,“雅言”一词已渐取“夏声” 而代之,原始义终为后起义所掩了。《荀子·荣辱》篇云:
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正可见“雅言”是士大夫的标准语,以别于各地的方言。 但是“雅言”并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涉及一定的文化内容。孔子“《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而礼、乐、诗、书在古代则是完全属于统治阶级的文化。这不恰好说明,所谓“雅言”便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吗?中国的“雅言”传统不但起源极早,而且一脉相承,延续不断,因此才能在历史上发挥了文化统一的重大效用。这在世界文化史上可以说是独步的。即使在政治分裂的时代,中国的大传统仍然继续维系着一种共同的文化意识。所以东晋南朝的士大夫和寒人,无论是北人或南人,都用洛阳语音来保存并传播他们的典雅文化。陈寅恪在《东晋南朝之吴语》中说:
除民间谣谚之未经文人删改润色者以外,凡东晋南朝之士大夫以及寒人之能作韵者,依其籍贯,纵属吴人,而所作之韵语通常不用吴音,盖东晋南朝吴人之属于士族阶级者,其在朝廷论议社会交际之时尚且不操吴语,岂得于其模拟古昔典雅丽则之韵语转用土音乎?至于吴之寒人既作典雅之韵语,亦必依仿胜流,同用北音,以冒充士族,则更宜力避吴音而不敢用。
这个历史结论正足以说明中国的“雅言”传统是多么地顽固。
如果“雅言”传统仅仅保存在“君子”、“士大夫”阶层的手中,和一般下层人民毫无关系,那么它在文化统一上的功能仍然是很有限的。以欧洲史为例,它的“雅言”是拉丁文,其传授则在学校,是属于上层贵族的文化。至于各地的人民则都用方言,可以和拉丁文互不相涉。欧洲的大传统和一般人民比较隔阂,成为一种“封闭的传统”(closed tradition) ,是不难理解的。 一般地说,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一方面固然相互独立,另一方面也不断地相互交流。所以大传统中的伟大思想或优美诗歌往往起于民间,而大传统既形成之后也通过种种渠道再回到民间,并且在意义上发生种种始料不及的改变。 但理论上虽然如此,在实际的历史经验中这两个传统的关系却不免会因每一种文化之不同而大有程度上的差异。和其他源远流长的文化相较,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文化大、小传统之间的交流似乎更为畅通,秦汉时代尤其如此。这种特殊情况的造成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上面所提到的“雅言”传统。中国的方言虽多,但文字的演变自商周以来大体上则一脉相承。王国维断定战国时六国用“古文”,属于东土系统,秦用“籀文”,属西土系统,但是他又说这两个系统“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 秦统一之后,李斯推行“书同文”的政策,更加强了文字统一的趋势。这个看法并不否认六国文字各有地方色彩的事实,更不是说中国文字在任何时期已取得完全的统一。这里所强调的只是中国文字远从商周以前起,大体上是沿着一个共同的系统而发展的。而且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考古的证据可以断定它不是起源于本土的。 所以有不少中国字,古今的写法仍相去不远,例如古文中的“文”、“字”两个字,今天依然一望可识。中国的“雅言”传统不能与欧洲拉丁文相提并论,其道理是很显然的。自六、七世纪蛮族入侵以来,相对于欧洲各地的方言来说,拉丁文实不啻为一种外国语文,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但不会读,不会写,而且也不会听。 中国的“雅言”则是本国语文的标准化或雅化,例如《诗经》中“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牛羊下来”之类的句子,即使是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完全听得懂。中国文化大、小传统之间互相通流恐怕和这一特殊的语文情况很有关系。汉代流行的两部字书——《尔雅》与《方言》——也有助于说明问题。《尔雅》所释的是“雅言”,属于大传统的范围;《方言》所释的是各地方的土语,自属小传统无疑。这两部字书正是沟通大、小传统的重要工具。《尔雅》不但以今语释古语,而且还以俗名释雅名,尤可见汉儒对小传统的重视。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很早便已自觉到大、小传统之间是一种共同成长、互为影响的关系。《论语·先进》: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此处“野人”指一般农民,“君子”指贵族士大夫,似无可疑。 “礼乐”自是古代的大传统。所以孔子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大传统起源于农村人民的生活。孔子说:“绘事后素。”(《论语·八佾》) 子夏听了,举一反三地问:“礼后乎?”孔子大为称赞。礼属后起,即起于生活的内在要求。总之,根据中国人的一贯观点,大传统是从许多小传统中逐渐提炼出来的,后者是前者的源头活水。不但大传统(如礼乐) 源自民间,而且最后又必须回到民间,并在民间得到较长久的保存,至少这是孔子以来的共同见解。像“缘人情而制礼”、“礼失求诸野”之类的说法其实都蕴涵着大、小传统不相隔绝的意思。
若以古代大传统中的经典而言,此一中国文化的特色更为显著。《左传》“襄公十四年”条说: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
《国语·周语上》也说: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
这种记载虽不免有理想化之嫌,但可见《诗》、《书》等经典中确反映了一些民间各阶层人的思想和情感。无论我们是否相信周代有“采诗”之事,《诗经·国风》中有不少诗起源于各地的小传统,在今天看来已成定论。至于汉武帝设立乐府之官,有系统地在各地搜集民间歌谣,则更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今天文学史家大概都不否认现存汉代乐府中有许多源出民间的作品。承担大传统的统治阶层对于各地的民间小传统给予这样全面而深切的注意,这在古代世界文化史上真可谓别具一格。《汉书·艺文志》在“诗赋家”之末论之曰: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可见乐府采诗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想要了解各地的风俗,而观察风俗则又是为“移风易俗”做准备的。这是整个儒家“礼乐教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与本文所研究的循吏关系甚大,下文当续有讨论。《孝经·广要道》章记孔子之语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此即汉代乐府制度的理论根据。汉儒所最重视的是文化统一,故宣帝时王吉上疏有云: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自董仲舒以来,所谓“春秋大一统”都是指文化统一而言,与政治统一虽有关而实不相同。用现代的观念说,移风易俗不能诉诸政治强力,只有通过长时期的教化才可望有成。但“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共俗”,倘不先深知各地传统之异而加以疏导,则大传统的教化亦终无所施。所以“观风俗”在汉代是一项极重要的政治措施,乐府采诗不过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应劭《风俗通义·序》说:“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汉书·地理志下》之末所辑各地的风俗便是成帝时丞相张禹使属下朱赣整理出来的。这是汉代中央政府的档案中藏有大量的风俗资料的明证。“观采风谣”在汉代绝不仅是“空言”,而确已“见诸实事”。班固《汉书》中所记是根据西汉时代的官方文书,而东汉以后政府仍在随时搜集各地风俗。《后汉书·方术·李传》载:
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
举此一例即可见汉代“观采风谣”制度的推行是极其普遍而认真的。使者“微服单行”便是为了掩饰他们的官方身份,唯有如此,各地人民才肯无所顾忌地说出他们内心的感情和想法。这个例子也为儒家理论在汉代的实践提供了真凭实据。
前已指出,“观采风谣”是儒家“礼乐教化”的预备工作,其目的在推动文化的统一。这种文化统一的努力当然有助于政治统一,因此才获得汉廷的积极支持。但是我们又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是专为便于皇帝专制而设计的制度。即使皇帝的动机是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我们也不应据此而否定儒家理论别有超越政治之上的更深含义。《汉书》卷五十一《贾山传》载他在文帝时所上的《至言》有云:
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瞽诵诗谏,公卿比谏,士传言谏(过),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
贾山的话显然本于前引《左传》“襄公十三年”条及《国语·周语上》所记邵公关于“防民之口”的议论。《左传》在前引文之后说:
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按:即“生”)?必不然矣!
可证“观采风谣”也含有限制帝王“一人肆于民上”的用意。所以《至言》特别强调“今人主之威”不下“雷霆万钧”,必须通过“观采风谣”以防止其滥用。
总之,儒家基本上是主张文化统一的,即以礼乐的大传统来化民成俗。这个教化的过程是以渐不以剧的。《汉书》卷四十三《叔孙通传》引鲁国两个儒生的话云:
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
颜师古注曰:
言行德教百年,然后可定礼乐也。
这两个儒生谨守孔子的旧义,所以终不肯曲学阿世,随叔孙通到汉廷去定朝仪。儒家关于礼乐教化的原始教义绝不是帝王专制的缘饰品,这可以从上引贾山的“至言”和鲁两生的言论中获得确切的证明。至于汉代朝廷实际上曾通过种种方式来以“儒术缘饰吏事”,那当然是另一个问题。
汉代儒家的大传统在文化史上显然有两种意义:一是由礼乐教化而移风易俗,一是根据“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理论来限制大一统时代的皇权。“观采风谣”在这两方面都恰恰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古代中国的大、小传统是一种双行道的关系,因此大传统一方面固然超越了小传统,另一方面则又包括了小传统。周代《诗经》和两汉乐府中的诗歌都保存了大量的民间作品,但这些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其一部分的原因则在于它们已经过上层文士的艺术加工或“雅化”。 这是中国大传统由小传统中提炼而成的一种最具体的说明。汉代大、小传统之间的交流尤其活泼畅遂,文人学士对两种传统的文献都同样加以重视。事实上,由于汉代的大一统开创了一个“布衣君相”的新局面,古代贵族社会已告终结,代之而起的则是以士、农、工、商为主体的四民社会。这一新局面在文化上所表现的特殊形态便是大、小传统互相混杂,甚至两者之间已无从截然划清界线。只要我们细读《汉书·艺文志》中刘歆的《七略》即可对当时的文化状态有一清楚的概念。
《七略》之中,术数和方技两类显然是民间小传统中的产品。六艺、诸子、诗赋三类似乎应该划在上层大传统之内。但一究其内容,则几乎没有一类不受到小传统的侵蚀。汉代的六经整个地在阴阳五行的笼罩之下,而阴阳五行根本便是长久以来流行在民间的观念,不过到战国晚期才受到系统化的处理而已。举例来说,《易》为六经之首,《艺文志》便明言“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孟喜是汉初易学大师,《汉书·儒林传》却告诉我们:“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王孙)且死时枕喜,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本文开始时引人类学家之说,大传统流入民间便会在意义上产生始料不及的变化。汉代的六经便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易经》如此,《诗经》亦然。《艺文志》说汉初训诗,“采杂说,咸非其本义”。这也是由于受到小传统的干扰,并不完全是因为一切“圣典”(sacred text)传衍既久必然因适应新情况而发生新解所致。 再就诸子九家而言,其中小说家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纯属小传统,故注引如淳曰:“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至于诗赋类中的乐府采自民间,上文已经讨论过了。
汉代以后,中国大、小传统逐渐趋向分隔,但儒家关于两个传统的关系的看法则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17世纪的刘献廷对于这一点有最明白的陈述。他在《广阳杂记》卷二说: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
从理论上说,刘献廷的话并不算新颖。《中庸》云:“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王阳明说:“与愚夫愚妇同的便是同德。”后来章学诚《原道》篇也说:“学于众人,斯为圣人。”圣人之“道”源出于百姓的人伦日用,这一点是古今儒家所一致肯定的。但是在刘献廷之前,从来未有人能这样明确而具体地把六经分指为以小说、戏曲、占卜、祭祀为前身。由于他的点破,儒家大传统和民间小传统之间的关系便非常生动地显露出来了。而刘献廷之所以有此妙悟,则又有其时代的背景。16世纪以来,由于商人阶层的兴起,城市的通俗文化有了飞跃的发展;戏曲小说便是这一文化的核心,因此才引起了士大夫的普遍注意。中国的大、小传统之间也再一次发生了密切的交流。
(二)汉代的大传统与原始儒教
汉代大、小传统之间的关系既明,循吏的特殊功能才可获得深一层的理解。雷德斐指出,所有的大传统都要通过教师(teachers) 传播到一般人民,他并且举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教人物和方式来说明他的论点。 但是汉代的大传统和有组织的宗教不同,它的教师也不是专业的宗教人物,如印度寺庙中的“诵经者”(reciters) 或伊斯兰教的“圣者”(saints)。本文的重点便是讨论汉代大传统的传布究竟具有哪些中国的特性。汉代的循吏毫无疑问地曾扮演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但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为什么传播大传统的责任在中国竟会落在循吏的身上呢?
首先我们必须从澄清汉代大传统的基本性质开始。雷氏所谓大传统主要指在某一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价值系统而言,这种价值系统往往托身于宗教,如西方的基督教或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但汉代大传统的形态则颇有不同,它不是通常意义下的“宗教”,尤与拥有正式的教会组织、专业的传教士以及严格的教条(dogmas) 那种形态的宗教截然有别。《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列举阴阳、儒、墨、名、法、道为汉初的六大思想流派,这大概可以代表当时的大传统。不过严格地说,在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则只有儒、道、法三家。由于汉代思想界已趋向混合,差不多已没有任何一家可以完全保持其纯洁性,而不受其他各家的影响。其中阴阳五行的观念则尤其如水银泻地,无所不在。不过阴阳五行说所提供的主要是一个宇宙的间架:儒、道、法三家虽都采用其间架,基本上却并未改变它们关于文化、政治、社会的理论内容。墨、名两家在汉代则已退居支流,可以存而不论。
儒、道、法三家之间也早已发生了交互影响,其间的关系甚为复杂。例如在政治思想方面不但黄老与申韩已合流,儒家也有法家化的倾向。 但以文化、社会价值而言,则我们不能不承认儒家在汉代大传统中的主流地位,道、法两家似不能与之争衡。顾炎武论“秦纪会稽山刻石”,特别指出:
然则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
顾炎武根据泰山、碣石门及会稽等地的刻石,指出秦始皇提倡三代礼教以矫正各地小传统中的风俗。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坚强的历史证据之上。可见在文化、社会政策方面,秦始皇仍不能不舍法家而取儒家。应劭《风俗通义》云:
然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以故礼乐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温饱完结,所谓治安之国也。
这是指摘汉文帝的黄老之治未能发挥移风易俗的积极功效。这一论断也是有根据的,虽然道家“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态度曾为儒家的教化导其先路。总之,从文化史的观点看,儒教在汉代确居于主流的地位,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用它来代表当时的大传统。但是从政治史的观点看,我们却不能轻率地断定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已变成了一个“儒教国家”(Confucian state)。儒教对汉代国家体制,尤其是对中央政府的影响是比较表面的,当时的人已指出是“以经术润饰吏事”。以制度的实际渊源而言,“汉承秦制”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有明白而详细的记载;法家的影响仍然是主要的。汉宣帝的名言云: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这是汉代政治未曾定于儒家之一尊的明证。儒教在汉代的效用主要表现在人伦日用的方面,属于今天所谓文化、社会的范畴。这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所以无形重于有形,民间过于朝廷,风俗多于制度。在这些方面,循吏所扮演的角色便比卿相和经师都要重要得多,因为他们是亲民之官。
儒教在中国史的不同阶段中曾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出现。汉代的儒教究竟具有什么特点?这是我们必须进一步说明的问题。从唐代的韩愈以来,很多人都相信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道统”在汉代中断了,因为以心性论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已被阴阳五行的系统取而代之。这个看法当然有相当的历史根据。不可否认,《孟子》、《中庸》以及《大学》中都有所谓心性论的成分。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韩愈以来儒家心性论的再发现是受佛教的刺激而起。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心性论为决定儒家道统的唯一标准呢?
本文不能讨论儒家道统论是否可以成立这个大问题。我们只想指出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即从战国到汉代,不但心性论尚未成为儒教的中心问题,孟子也还没有取得正统的地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和《儒林列传》都是第一手的证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云:
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这一段话的解释向来争论很多,此处不能详及。但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十六说:
孔、墨同称,始于战国,孟、荀齐号,起自汉儒,虽韩退之亦不免。(原注:见《进学解》)盖上二句指荀卿,即传所谓荀子推儒、墨道德行事兴坏著数万言者,下二句指孟子,《儒林传》言孟子、荀卿咸遵夫子之业,非孟、荀并列之证欤?夫荀况尝非孟子矣,岂可并吾孟子哉!
梁玉绳的话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他已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后世孔、孟正统的观念,因此在情绪上他无法承认批评孟子的荀况“可并吾孟子”。但是他是《史记》的专家,客观的证据逼使他不能不得出“孟、荀齐号,起自汉儒”的结论。《史记·儒林列传》上所载“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的事实是没有办法否认的。不但如此,以西汉一代而论,荀子在儒教中的重要性恐怕还在孟子之上。
本文是历史的研究,孟、荀孰得孔子的嫡传,在此无关紧要。我们所重视的则是司马迁所说的孟、荀“咸遵夫子之业”那句话。换句话说,在汉代人的理解中,孟、荀两家都承继了孔子的儒教,他们之间的相同处远比相异处为重要。本文论汉代儒教则根据两个标准:第一,在先秦儒教传统中,孔、孟、荀三家的共同点是什么?第二,汉儒接受先秦儒教并且见之于行事的究竟是哪些部分?只有通过这两个标准的检验,我们才能比较有把握地确定汉代儒教的基本内容,也只有这样的儒教才有资格被称为“大传统”。中国思想自始即不以抽象思辨见长,儒家尤其如此。所以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 儒家教义的实践性格及其对人生的全面涵盖使它很自然地形成中国大传统中的主流。这个大传统不但事实上在汉代没有中断,而且儒教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的支配力量,其基础正是在汉代奠定的。汉代儒教和阴阳五行之说相混杂确属事实。例如董仲舒以后,儒家多说“天人相应”,并以阴阳配情性、五行配五常。凡此之类,不可胜数,其大异于先秦儒家的立论是无可讳言的。从严格的哲学观点看,我们当然可以说儒家已“失传”了。但是从文化史或广义的思想史的观点看,这种情形恰足以说明儒教在汉代是一个有生命的大传统,因为它真正和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合流了。前面已经指出,依人类学家的观察,大传统一旦落到下层人民的手上便必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因而失去其原义。不但汉代如此,明代的王学也是一样。黄宗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又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后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黄宗羲从严格的哲学观点为阳明惋惜,但是我们却正可由此而断定王学在晚明是充满着活力的大传统。而且更深一层分析,阴阳五行说对先秦儒教的歪曲其实仅限于它的超越的哲学根据一方面,至于文化价值,如仁、义、礼、智、信之类,则汉儒大体上并没有改变先秦旧说。事实上,孝悌观念之深入中国通俗文化主要是由于汉儒的长期宣扬。汉儒用阴阳五行的通俗观念取代了先秦儒家的精微的哲学论证,但儒教的基本教义也许正因此才冲破了大传统的樊篱,成为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道理。
以上我们试图从大、小传统的关系着眼,说明汉代儒教何以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大传统。从纯哲学的观点说,汉代儒教自是“卑之毋甚高论”,但它确曾发挥了“移风易俗”的巨大作用。中国文化流布之广、持续之久和凝聚力之大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而儒教在这一文化系统中则无疑是居于枢纽的位置。无论我们今天对儒教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这个历史事实都是无法抹杀的。《中庸》描写儒家的“至圣”有云:
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
这在《中庸》作者的时代尚不过是一种高远的想像,然而自汉代以后,孔子和他所开创的儒教在中国甚至东亚的世界中几乎已达到了这个想像的境界。在这一化想像为现实的历史进程中,两汉的儒家,包括循吏在内,是一批最重要的先驱人物。
根据上面所设立的两个标准,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指出,从孔、孟、荀到汉代,儒教的中心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文化秩序。孔子以前的中国大传统是所谓三代的礼乐,即《论语·为政》所说“周因于殷礼、殷因于夏礼”的文化系统。这个系统在春秋时代已陷于“礼坏乐崩”的局面,但孔子仍然向往周代盛世的礼乐秩序;他一生最崇拜的古人则是传说中“制礼作乐”的周公。所以他说: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但孔子深知“礼”是随着时代的变动而必然有所“损益”的,所以他的“从周”决不能理解为完全恢复周公的礼制。从“其或继周者,百世可知也”的话来看,他不过是主张继承周公的精神以推陈出新而已。他曾这样描写理想中的文化秩序: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刑法”是孔子时代所出现的新事物,但孔子在这里仅指出“政”与“刑”之不足,而不是完全否定它们的功效。孔子的理想秩序则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是他“继周”而加以“损益”之所在。这两种秩序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最低限度与最高限度的分别。用现代的观念说,孔子所希望重建的主要是道德、文化的秩序;这是最高限度的秩序,超越但同时也包括了最低限度的政治、法律的秩序。所以对孔子和儒家而言,文化秩序才是第一义的,政治秩序则是第二义的。孟子、荀子至汉代的循吏都接受这一共同的原则。
如所周知,孔子明确地提出“仁”为“礼”的超越根据是一个最重要的贡献。正是由于这一贡献,他才能在古代礼乐的废墟上创建了儒教。“仁”是“礼”的内在的精神基础,“礼”是“仁”的外在的形式表现。这是孔子以来儒教的通义。后起的孟、荀两家虽有畸轻畸重的差异,然皆莫能自外于此一通义。但是礼治或德治的秩序究竟通过何种具体的程序才能建立呢?传统的看法是用《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说明儒教从“内圣”到“外王”的具体步骤。前四条是战国中晚期各家修身论竞起的结晶,此处姑且置之不论, 但修、齐、治、平之说则在《论语》、《孟子》、《荀子》中都可以获得印证。照这个看法,似乎儒家的德治秩序完全是从统治者个人的道德修养中逐步推出来的。自《庄子·天下》篇提出“内圣外王”的观念以后,儒家的德治论便普遍地被理解为“内圣”必然导致“外王”或“内圣”是“外王”的先决条件。我们必须承认,儒教的确要求统治阶层的所有成员都“以修身为本”。在先秦至两汉的儒家议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修身”是特别针对着“士”而设的说教。对于“士”以及“士”以上的人来说,修、齐、治、平是一个必要的程序。汉代以“孝悌”为取士的最重要的标准,便是根据“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的逻辑推衍出来的。无可讳言,儒家坚信“士”是文化的“先觉”,具有特殊的历史使命——即“以此道觉此民”,而“自任以天下之重” 。从现代的观点看,这当然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精英论”(elitism)。在儒教的支配之下,“士”在中国文化的长期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这是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但是修、齐、治、平的程序并不适用于一般“后知”、“后觉”的人民。从社会的整体的角度出发,儒家德治秩序的建立则依循另一套程序。《论语·子路》: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这个“先富后教”说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而先后为孟、荀所承继。 孟子曾一再向当时的国君强调“仁心”,又曾明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这都合于修、齐、治、平的程序。但是他向齐宣王论“仁政”却说:
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这正是对“先富后教”说的进一步的发挥。孟子在他对尧的时代加以理想化的时候,也说:
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可见,从人民的群体生活着眼,儒家的德治秩序必须首先建立在“饱”、“暖”的基础之上。只有在“黎民不饥不寒”(此语两见于《孟子·梁惠王》上)以后才能谈得到“礼义”的教化。“先富后教”是儒家的通义,也可以从《尚书·洪范》中得到证实。《洪范》成篇的时代在此无须讨论,但作为一篇重要的儒家文献,它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在《洪范》的“八政”之中,“食”居首位,“货”为其次,“司徒”则列第五。据郑玄注,“此数本诸其职先后之宜也”。所以“八政”的次序是出于有意义、有计划的安排,与“先富后教”完全一致,更和上引《孟子·滕文公》之说若合符节。不但儒家如此,受儒家影响的《管子·牧民》篇也开宗明义地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荀子的“礼治”论与孟子的“仁政”说虽有外倾与内倾之别,但荀子对“修身”的重视并不在孟子之下。他在《君道》篇说:“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他的《修身》篇更是完全针对“士”而发,故有“士欲独修其身”之语。可见从“修身”推到“治国”也是荀子所肯定的程序。近人多以《大学》出于荀子的系统,似乎是有根据的。但是荀子讲“修身”,其出发点仍然是在“君”或“士”的个人。荀子生活在秦代统一中国的前夕,因此他最关心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建立一个“相与群居而无乱”(《礼论》) 的社会。他所提出的答案则是“礼”。《礼论》说: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这是最广义的“礼”,也就是一种礼治秩序。在这个秩序中,荀子所强调的则是“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即满足人民的物质欲望。但是为了使人人的欲望都能获得适当的满足,“礼”的节制作用是不可少的。换句话说,只有寓“养”于“礼”才能建立起一个“群居而无乱”的秩序。礼治的目的既在于“养”,因此“富国”必然归结到“富民”。《富国》篇说: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按:当是“节用”之讹)故多余,裕民则民富。
尤其重要的是他所说的“民”是一般老百姓。《王制》篇说:
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
这是儒家“藏富于民”的主张。财富不但不应该集中在任何特殊阶级之手,而且更不应该集中在政府之手。“府库实而百姓贫”乃是“亡国”的象征。在《王制》的“序官”一节中,荀子也先列“治田”,次及“养林”,然后才说到“教化”。他论“乡师”云:
顺州里,定廛宅,养六畜,闲树艺,劝教化,趋孝弟,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乡师之事也。
这是荀子理想中农村的礼治秩序。故《王制》序官之法与《洪范》之首序食、货之官,后及司徒教民之职,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按:《荀子·王制》中的“司徒”不掌教民,与《孟子》、《洪范》的“司徒”不同。读者宜注意。)
我们在上文讨论儒家德治或礼治秩序的建立,指出其中有两个相关但完全不同的程序。第一个程序是从“反求诸己”开始,由修身逐步推展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二个程序则从奠定经济基础开始,是“先富后教”。前者主要是对于个别的“士”的道德要求。这是因为“士志于道”(《论语·里仁》),“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而后者则是维系人民的群体秩序的基本条件。正如荀子所说,“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儒效》篇) 。对于一般人民而言,只有“先富后教”的程序才是他们所能接受的。这两种程序当然有内在的关联性:“士”是四民之首,平时在道德和知识方面都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在机会到来时才能执行“富民”、“教民”的任务。孟子说得最清楚:
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所以儒家“修身”的最后目的永远是“泽加于民”。
但是在实践中,这两种程序决不可加以混淆。关于这一点董仲舒早已给予一个最透彻的分析。他把这两种程序分别称之为“仁”与“义”。《春秋繁露·仁义法二十九》开头便说:
《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
“仁义法”在实践中究竟怎样区别呢?他说:
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顺逆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祉(原注:一作“礼”)以劝福(原注:一作“赡”);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孔子谓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语樊迟曰:“治身者先难后获,以此之谓。治身之与治民,所先后者不同焉矣。”《诗》云:“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辐,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后其食,谓之治身也。
可见“修身”是“内治”的程序;“先富后教”则是“外治”的程序。这两个程序之间的界线一旦混乱了,便会发生可怕的社会后果:
是故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为礼不敬也。为礼不敬则伤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宽则伤厚而民弗亲。弗亲则弗信;弗尊则弗敬。
“内治”与“外治”两个程序的混淆一直是中国儒教史上一大问题,到今天还没获得彻底的澄清。从上引董仲舒的议论中,我们不难看到,这种混淆早在汉初便已存在了。宋明理学的内倾性格更加深了一般人对儒教的误解。“存天理、灭人欲”以“希圣希贤”是“内治”或“治身”的语言,只有对于个别的“士”才有意义,如果误用在“外治”或“治民”的程序上,便必然流于戴震所谓“以理杀人”了。 原始儒教在理论上承认“人皆可以为尧舜”或“涂之人皆可以为禹”,但是决不要求人人都成圣成贤。因此,在“治民”的程序上,它的主张只是“宽制以容众”,“先富之而后加教”。
但汉代毕竟去古未远,当时的儒者大体上仍对原始儒教的基本方向有比较亲切的了解。这种了解使他们明确地意识到,他们的历史使命是建立一个“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文化秩序,其具体的进行程序则是“先富之而后加教”。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效》篇) 一般地说,汉代的儒者至少在观念上接受了这个规定。循吏则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他们的“教化”工作便是对儒家原始教义的实践。用现代的观念说,循吏是大传统的承担者;在政治统一的有利条件下,他们把大传统广泛地传布到中国的各地区。但是他们从事文化传布的努力是出于自觉的,因为他们的工作的内容和方式与原始儒家教义之间的一致性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决不能以偶然的巧合视之。我们在上文之所以详论孔、孟、荀以至董仲舒诸家的思想便是为了说明这一点。
以下我们将转入汉代循吏的研究。
(三)“循吏”概念的变迁
“循吏”之名始于《史记·循吏列传》,而为班固《汉书》和范晔《后汉书》所承袭。从此“循吏”便成为中国正史列传的一个典型,直到民国初年所修的《清史稿》仍然沿用不变。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史中的“循吏”,若细加分析,其含义仍各有不同,尤以《史》、《汉》之间的差别为最值得注意。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
同书《循吏列传》开宗明义说:
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这两段话大致可以代表司马迁的循吏观。但在进一步分析之前,我们必须对《史记·循吏列传》在传统史学上所引起的若干重要疑点略加疏解。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十五“循吏列传”条云:
史公传循吏无汉以下,传酷吏无秦以前,深所难晓。
明末陈子龙已说过同样的话,不过他的结语是“寄慨深矣”四个字。 《史记·循吏列传》共收五人,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这一点曾引起各种推测。司马迁著史必有“微言大义”在内,这是后代专家大致都承认的。这一看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司马迁在《自序》中不但提出了《史记》是否上承《春秋》的问题,并且故作“唯唯否否”之词。但是我们虽然可以肯定《循吏列传》的特殊写法含有某种“微言”,却已无法确定这个“微言”究竟是什么了。方苞《史记评语》“循吏列传”条说:
循吏独举五人,伤汉事也。……史公盖欲传酷吏,而先列古循吏以为标准。……然酷吏恣睢实由武帝侈心,不能自克,而倚以集事。故曰:身修者官未曾乱也。
这是说,司马迁写循吏传故意只列古代人物以反照汉代但有酷吏。所以《循吏列传》事实上是史公对汉武帝的“侈心”表示一种深刻的批评。另一种见解则恰好与此相反。《史记会注考证》卷一二○《汲郑列传》引宋代叶梦得之言曰:
循吏传后即次以黯,其以黯列于循吏乎?而以郑当时附之。黯尚无为之化,当时尚黄老言,亦无为云。
这是以汲黯、郑当时为汉代的循吏,故《循吏列传》并不是“无汉以下”,如梁玉绳或方苞所云。日本学者颇有相信此说者。泷川氏在同书卷六十一《伯夷列传》卷首“考证”下即说:
《循吏列传》后叙汲黯、郑当时者,以两人亦循吏也。
冈崎文夫也推断汲、郑两人是“奉法循理”的循吏,并特别指出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好黄老言”。 但此外还有第三个看法,《史记志疑》卷三十五引陈仁锡《史诠》云:
汉之循吏,莫若吴公、文翁,子长不为作传,亦一缺事。
这是以《史记》无汉代循吏乃出于史料搜集之疏漏,未必是司马迁有意如此。
以上三种看法各有理由,但也各有困难,此处不能详说。本文不想在《史记》无文字之处再添一种推测,兹就《史记》本文略加分析,以澄清司马迁的循吏观。我们试读上引《太史公自序》中“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几句话,便可发现他对循吏的描写完全是负面的;他只强调循吏在消极方面不做什么,却无一语道及他们在积极方面究竟做什么。他在《循吏列传》记述鲁相公仪休也说:
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这仍然是强调“无”、强调“不”,全从反面落笔。我们看了这些文字,似乎可以推断司马迁心中的循吏是汉初文、景之世黄老无为式的治民之官。我们必须记住一个重要的事实:司马迁生活在酷吏当令的武帝时代,因此他没有机会看到昭、宣以下那种“先富后教”型的循吏。他对酷吏的深恶痛绝确是情见乎辞的,故不但《循吏列传》有“何必威严”之语,《酷吏列传》的序论更是立场鲜明。序文是这样开端的: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
司马迁引孔、老两家之说,显然是针对武帝过分重视政刑法令而发。但是他自己的政治倾向似乎仍是在道家的一边,所以“导之以德”之“德”在他的理解中即是“上德不德”。换句话说,他是主张“我无为而民自化”的。后人惋惜《史记·循吏列传》不收吴公、文翁两人,则是因为他们受了《汉书·循吏传》的影响。班固说:
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
但事实上,吴公其人正是由于《史记》才流传下来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
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
可见吴公是李斯弟子,渊源在法家。司马迁提到吴公主要是因为他是贾谊的推荐者。他究竟是否符合史公心中的循吏标准,今已不可知。无论如何,史公并没有称他为循吏,称吴公为循吏的是东汉的班固。文翁为蜀郡太守则始于景帝末,与史公同时而稍早,且其人终生在蜀,位亦未至公卿。司马迁撰史时或尚不详其事迹,故《司马相如列传》中也没有提及文翁。总之,详考《史记》本文,我们只能获得一个比较确定的结论,即终司马迁之世,积极从事于教化工作的循吏尚未成为普遍的典型。所以司马迁所谓“循吏”主要是指文景时代黄老无为式的人物,后来儒家型的循吏观念在他的心中似乎尚未十分明晰。司马迁谈论六家要旨有云: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此处“因循”两字即是《史记》“循吏”之“循”的确诂。
《汉书·循吏传》云:
孝武之世……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数谢病去,弘、兒宽至三公。
可见汉武帝完全是从粉饰太平的观点来提倡儒教的,至于儒家“养民”、“教民”的基本教义则好像并没有博得他的同情。《汉书·循吏传》续言:
及至孝宣,由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
上引班固两段叙事自是实录。教化型的循吏辈出确在宣帝之世。《史记》中的循吏和宣帝以下的循吏虽同名而异实,其中一个最显著的区别便是前者是道家的无为,而后者则是儒家的有为。“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绝不是仅仅“奉法循理”所克幸致,而是只有通过积极的努力才能取得的收获。
两汉书论循吏和酷吏的消长以及政风的变迁都归因于个别君主的政治倾向与不同时期的社会状态,而后世论者尤重视君主的影响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当然是很密切的,否则何以酷吏多出现在武帝之世,而循吏却偏偏以宣帝之世为最盛? 但是除了帝王个人和时代的因素之外,我们也必须注意地域性的差异。中国各地风俗不同,有宜于宽治而用循吏者,有宜于严治而用酷吏者;更有宜先严后宽或先宽后严者,则循吏、酷吏交互为用。如卫地的东郡,据《汉书·地理志下·风俗》篇云:
其俗刚武,上气力。汉兴,二千石治者亦以杀戮为威。宣帝时韩延寿为东郡太守,承圣恩、崇礼义、尊谏争。至今东郡号善为吏,延寿之化也。
这便是先严后宽的一例。《后汉书·循吏列传》序论说:
若杜诗守南阳,号为杜母,任延、锡光移变边俗,斯其绩用之最章章者也。
后汉的循吏在边郡的政绩确很突出,这也和地域性有关。但他们的任用并不限于边郡,南阳在后汉是所谓“帝乡”,当然不能算是边郡。《汉书·地理志下》“韩地风俗”条下云:
南阳好商贾,召父(召信臣)富以本业;颍川好争讼分异,黄(霸)、韩(延寿)化以笃厚。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
尤可证虽同为循吏,但因有地域性之别,教化之道也随之而各有不同。所以班固在《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中说:
谁毁谁誉,誉其有试。泯泯群黎,化成良吏。淑人君子,时同功异。没世遗爱,民有余思。述循吏传。
循吏之所以“时同功异”,正由于他们的具体工作是因地制宜、不拘一格的。但是班固对循吏的赞词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最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汉代会出现这么多以“化民成俗”为己任的“淑人君子”呢?我们能满意于已有的一些简单答案,例如说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或者说这是“吏治视上之趋向”所使然吗?像循吏这样的人物是仅仅由于朝廷的提倡奖励便能在短期内塑造得出来的吗?
(四)循吏教化与汉廷政策
中外学者研究汉代循吏都是从政治制度的观点出发,所以往往以酷吏与循吏相对照。汉家制度自始便是“以霸王道杂之”,汉高祖十一年二月诏书并举周文王与齐桓公为典范(《汉书·高帝纪》下),实已露王霸兼采的端倪。 终两汉之世,循吏和酷吏两大典型虽因各时期的中央政策不同而互为消长,但始终有如二水分流,未曾间断。从思想源流的大体言之,循吏代表了儒家的德治,酷吏代表了法家的刑政;汉廷则相当巧妙地运用这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力量,逐步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秩序。
关于汉代循吏的政治功能,已经有人讨论过了,本文不想多说, 本文所特别重视的则是循吏的文化功能。与酷吏相比较,循吏显然具有政治和文化两重功能。循吏首先是“吏”,自然也和一般的吏一样,必须遵奉汉廷的法令以保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作。但是循吏的最大特色则在他同时又扮演了大传统的“师”(teacher)的角色。上文已说明,汉代的大传统以儒教为主体,而儒教的基地则在社会而不在朝廷。因此循吏在发挥“师”的功能时,他事实上已离开了“吏”的岗位;他所奉行的不复是朝廷法令,而是大传统的中心教义。由于中国的大传统并非寄身于有组织的宗教,所以它的传播的任务才落到了俗世人物的循吏的肩上。汉代大传统的传播者,借用《周礼》的名词,可称之为“师儒”;循吏便是以“师儒”的身份从事“教化”工作的。循吏自然不是大传统的唯一传播者,但在汉代,“师儒”之中,循吏却是教化成绩最为卓著的一型。
在上一节中,我们曾指出,《史记》中的“循吏”基本上是黄老一派的道家观念;司马迁撰史时,《汉书》所载的儒家型的循吏尚未引起普遍的注意。《汉书·循吏传》中所载虽仅寥寥数人,但多在宣帝之世。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断言儒家型循吏的出现完全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呢?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汉武帝正式提倡儒学对于儒家型循吏的出现可能发生了激励的作用。但是事实俱在,循吏毕竟另有独立的文化传统,不能简单地看作汉廷政策的产品。在这一节里,我们将根据文翁、兒宽、韩延寿三人的传记资料来说明汉代循吏教化的起源及其与汉廷之间的复杂关系。
《汉书·循吏传·文翁》说: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閤。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汉代循吏“所居民富”,即执行孔子“富之”而后“教之”的规划,文翁自然也不是例外。《汉书》未记其“富民”的事迹,但《华阳国志》卷三云:
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顷。
《华阳国志》大约根据地方记载,足补《汉书》之略,不过文中误“景帝”为“文帝”而已。所以把《汉书》与《华阳国志》合起来看,文翁完全合乎宣帝以后儒家型循吏的标准。
但是文翁守蜀郡在景帝之末和武帝初年,尚在汉廷正式定儒学于一尊之前,他的推行教化绝不可能是奉行朝廷的旨意。文翁和汲黯、郑当时约略同时,如果说那时已有循吏,则汲黯、郑当时比文翁更具有代表性。以汲黯为例,他任东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静”,后来位列九卿也依然遵守“治务在无为”的原则(见《史记》本传) 。这种循吏合乎《史记》所谓“奉法循理”、“百姓无称”的标准,但显然与《汉书》所谓“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典型截然不同。换句话说,在文翁的时代,循吏的特征是“因循”和“无为”,因为这才符合文、景两朝崇尚黄老之治的要求。文翁在蜀实行教化则是本于他个人平素所持的信念,这种信念只能源于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儒教大传统。严格地分析,上引《文翁传》中所描述的设施已不在郡守职务的范围之内,文翁所发挥的也不是“吏”的功能,而是“师儒”的作用。文翁的例子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循吏兼具“吏”与“师”的双重身份。文翁的郡守职权虽然曾给他的教化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吏”与“师”两种功能却又不是混而不分的。“吏”的基本职责是维持政治秩序,这是奉行朝廷的法令;“师”的主要任务则是建立文化秩序,其最后动力来自保存在民间的儒教传统。用汉代的语言来表示,这一分别即是“政”与“教”的不同。汉代有关地方行政的文献往往以“政”与“教”并提,其中“教”字的含义颇不简单,下文将另有分疏。本文讨论循吏的文化意义,其重点则放在“教”的方面。
《文翁传》说汉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这一点十分重要,足以说明文化对政治的影响。文翁设立郡学显然是根据古代的庠序传统,当时的汉廷还没有制定一套普遍的教育政策。相反地,后来武帝立天下郡国学官倒是闻文翁之风而起的。 不但如此,我们还有理由相信,汉代的太学制度也有取于文翁郡学的规模。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事在元朔五年(西元前124年),是为太学之始(见《汉书·武帝纪》) 。《汉书·儒林传序》: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学将学生分为两等,高第为郎,次补文学掌故,和文翁所订“学官弟子……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的规章几乎如出一辙。这一制度上的相合恐非出于偶然。武帝立太学与立郡国学官同时,而郡国学官的实行则“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亦见《儒林传序》) ,所以我们推测太学曾取法于文翁的规制,根据是相当坚强的。总之,文翁的例子不但说明了循吏的历史渊源,而且也透露了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文化背景。战国以来,儒教已逐渐在中国的大传统中取得了主导的地位,“先富后教”早已成为汉代一般儒生的天经地义。袁文(1119~1190)《瓮牖闲评》卷一云:
汉儒记郑子产之事曰: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之。《左氏传》乃云:我有子弟,子产诲之。
袁文这条笔记的本意是在纠正汉儒对子产的误解,指出子产不仅“富民”,而且也“教民”,但是我们却恰可从汉儒的误解中看出他们的“教化”意识植根之深。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公孙弘的倡立太学和文翁的化蜀都来自一个共同的源头,即大传统的儒教。汉代的皇帝终于承认儒教的正统地位,与其说是由于儒教有利于专制统治,毋宁说是政治权威最后不得不向文化力量妥协。儒教大传统对于皇权的压力早在汉初便已见端倪。《史记》卷九十七《陆贾传》载: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
这个著名的故事极富于象征的意义,最能显示帝王对儒教所持的两难心理。“不怿”是不甘向儒教低头,“惭色”则是不得不承认儒教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是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出身“无赖”的汉高祖尚且如此,早年已接触过儒教的武帝更可想而知。武帝接受儒教也许主要是出于“缘饰”的动机,但肯定儒教在各家之中最具“缘饰”的作用即是承认它是大传统中的支配力量。欧洲中古的“君权神授说”也与此相类,俗世君主同样假基督教为“缘饰”之用。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正好证明基督教已取得大传统的主宰地位,以致政治势力也不得不借重它的精神权威。
汉武帝时,兒宽任左内史,领京畿诸县,他的措施完全合乎循吏的典型。《汉书》卷五十八本传说:
宽既治民,劝农桑,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宽表奏开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以故租多不入。后有军发,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襁属不绝。课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宽。
循吏具有“吏”和“师”的双重身份。“吏”的身份要求他执行朝廷的法令,“师儒”的身份则要求他以“仁爱”化民。但这两重身份发生抵触时,他往往舍“法令”而取“仁爱”。这是汉代循吏的特征。所以兒宽收租税时“与民相假贷”,不能完成“法令”所规定的任务,要受到免职的处分。相反地,酷吏则不惜用严厉的刑罚以执行朝廷的“法令”。宣帝时代酷吏严延年的母亲斥责其子曰:
幸得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爱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顾乘刑罚,多刑杀人,欲以立威,岂为民父母意哉!
这位严老太太所根据的正是儒教大传统中的“循吏”理想,认为郡守的最主要的责任是“仁爱教化”,可见兒宽在左内史任内的施政方针,其动力乃来自当时的大传统而不是号称“独尊儒术”的朝廷。兒宽的儒家背景在《汉书》本传中有清楚的说明:
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颜师古注:供诸弟子烹炊也。)时行赁作,带经而鉏,休息辄诵读,其精如此。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时张汤为廷尉,廷尉府尽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宽以儒生在其间,见谓不习事,不署曹,除为从史,之北地视畜数年。
可知武帝时代的汉廷尚是“文史法律之吏”的天下,以致兒宽以“儒生”厕身其间,落落寡合。武帝后来对他的赏识显然是由于他竟能由“负租、课殿当免”一跃而为“课更以最”。左内史治下的人民自动向政府缴租税,使他能超额完成“吏”的任务,这是武帝始料所不及的。换句话说,他受知于武帝仍在于他是一个能执行法令的能吏,而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仁爱教化”的循吏。
不但武帝时如此,下逮宣帝之世,情况依然未变。《汉书·循吏传》中人物虽多出宣帝一朝,但这只是表象,不足以为宣帝认真奖励循吏之证。韩延寿的事迹颇能说明礼乐教化和朝廷法令之间的紧张关系。
韩延寿名不列《汉书·循吏传》,但以推行教化而论,他的成绩和影响在西汉循吏中却是无与伦比的。他出身郡文学,深受儒教的熏陶,因此每出守一郡,必以移风俗、兴礼乐为治民的先务。《汉书》卷七十六本传记他任颍川太守云:
颍川……民多怨仇,延寿欲更改之,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
本传又记他稍后任东郡太守时的业绩云:
延寿为吏,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设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
可证韩延寿确是一直非常认真地在实行着儒家的礼乐教化,他的一切设施完全符合孔子所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原则。不但如此,他还深信当时大传统中“良吏为民之表率”的理论。所以史载他在东郡:
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约誓明,或欺负之者,延寿痛自刻责:“岂其负之,何以至此?”吏闻者自伤悔,其县尉至自刺死。
最后,在左冯翊任内,行县至高陵,适民有兄弟为田产争讼,韩延寿自责“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乃“入卧传舍,闭思过。一县莫知所为,县丞、啬夫、三老亦皆自系待罪”。直到这两个弟兄悔过息讼之后,他才“起听事”。本传说他在左冯翊时:
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复以辞讼自言者。推其至诚,吏民不忍欺绐。
《论语·卫灵公》: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又《颜渊》篇: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韩延寿正是自觉地实践了这一类的教言。毫无可疑地,他自始至终都是以“师儒”自居的,如制订丧祭嫁娶之礼、止兄弟之讼、“痛自刻责”、“闭思过”之类的举措都和他的“吏”的功能无直接关系。汉代郡守的主要职责,除了前引《兒宽传》所说的征收租税外,则以典刑狱、缉盗贼、制豪强为重点所在。 这些都是维持政治秩序的基本工作。但是韩延寿“为吏,上礼义,好古教化”,显然是以建立文化秩序为中心的旨趣。严格地说,他在各郡的措施已远超出“吏”的职务,其历史的意义只有从大传统的“师”的角度才能获得适当的理解。
以西汉的循吏教化而言,韩延寿的影响最为深远。《汉书·地理志·风俗》篇“颍川”条云:
韩延寿为太守,先之以敬让,黄霸继之,教化大行。
又东郡条也说:
宣帝时韩延寿为东郡太守,承圣恩,崇礼义,尊谏争。至今东郡号善为吏,延寿之化也。
《风俗》篇是颍川朱赣奉丞相张禹之命而辑成,即在河平四年与鸿嘉元年之间(西元前25~前20年)。其时上距韩延寿之死(五凤元年,西元前57年)不过三十多年,且朱赣即颍川人,所记本乡近事断无不可信之理。黄霸是宣帝时代最著名的循吏,且以治颍川为天下第一,累迁至丞相。今据《地理志》此条,则知颍川的教化已先在韩延寿任内奠定了基础。《韩延寿传》也明说:
黄霸代延寿居颍川,霸因其迹而大治。
不但如此,刘向(西元前79~前8年)与韩延寿同时而稍后,他在《新序》中也特别表扬赵广汉、尹翁归和韩延寿三人在三辅的治绩。 《新序》旨在“正纲纪、迪教化”,可见教化成绩在当时确是有目共睹的。
汉宣帝虽说过“霸王道杂之”的名言,但是他其实并不很欣赏“王道”。《汉书·元帝纪》明言“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萧望之传》则说他“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此外类似的记载也见于盖宽饶与匡衡两传。而且如果不是受到嫡庶制度的阻挠,他早已舍“柔仁好儒”的元帝,而改立“明察好法”的淮阳王为太子了(见《元帝纪》及《韦玄成传》)。所以宣帝表面上对循吏教化的敷衍正可看作政治势力不得不向代表着大传统的儒教妥协。他在循吏之中独取黄霸也是别有隐情的。《黄霸传》云:
霸少学律令,喜为吏。……为人明察内敏,又习文法,然温良有让,足知善御众。为丞处议,当于法,合人心。
这正合乎宣帝所赏识的“文法吏”的典型,而与韩延寿那种“上礼义,好古教化”的儒家型的循吏,截然异趣。
韩延寿的悲剧结局尤足以说明循吏的教化和汉廷法令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内在矛盾的。据《汉书》本传,韩延寿最后在左冯翊任内和御史大夫萧望之发生了严重冲突,彼此互揭罪状。但是他败诉了,结果是“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恶之,延寿竟坐弃市”。这是两汉时代一件大狱,所以稍后扬雄在《法言》中还特别举“韩冯翊之萧”为“臣自失”之一例(卷十《重黎》篇) 。我们今天已无法判断此案的真相, 但是“狡猾不道,天子恶之”的话则特别值得注意。韩延寿的罪状中以下列两项最为重要:第一是他在东郡太守任内为“都试讲武”之礼,竟成为“僭上不道”。韩延寿因“好古教化”而推行礼乐,不料反因此引起了宣帝的疑忌。汉代郡守权重,本已使朝廷不安。这一点后文当另有说明。韩延寿以教化而颇得吏民之心,自然更容易招祸了。他的第二大罪状是“取官钱帛,私假徭役吏民” 。颜师古解此句的“假”字为“顾赁”,这和他注《食货志上》“分田劫假”之“假”作“赁”大体一致,但其意义尚欠明晰。其实“假”字当解为“假贷”之意,与前引《宽传》中“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之“假贷”,意义完全相同。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韩延寿擅将公家的钱假贷给吏民以供徭役。从儒家教化的观点说,这正是一种爱民的德政,但是以朝廷法令而言,则反而成为郡守假公济私以收买民心的一大罪状了。韩延寿受刑的动人一幕尤其显示出他是怎样得到吏民的衷心爱戴。《汉书》本传记载道:
吏民数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车毂,争奏酒炙。延寿不忍距逆,人人为饮,计饮酒石余。使掾吏分谢送者:“远苦吏民,延寿死无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寿三子皆为郎吏,且死,属其子勿为吏,以己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
左冯翊这数千吏民显然是以集体的行动对朝廷表示了最强烈的抗议。韩延寿的礼乐教化渊源于当时的大传统,然而却与朝廷关于“吏道”的规定发生了基本的抵触。他以大传统的“师儒”自居,每治一郡便运用“吏”的职权来建立文化秩序。但是他料不到竟因此而招来“狡猾不道,天子恶之”的大祸,以至“弃市”,难怪他临刑时心灰意懒,要戒其子“勿为吏”了。由此可见,循吏虽兼具“吏”与“师”的双重身份,但是这双重身份却不是永远融合无间的。概略言之,“吏”代表以法令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师”则代表以教化为主的文化秩序;用中国原有的概念说,即是“政”与“教”两个传统,也可以称之为“政统”与“道统”。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关系是不即不离的,一方面互相支援,一方面又不断发生矛盾。汉代的循吏恰好处在这两个传统的交叉点上,因此循吏的研究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中的政教关系。下面我们要接着分析这两个传统在“吏道”观念上的根本分歧。
(五) 两种吏道观的对照
《尚书·泰誓上》云: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孔传》释此语说:
天佑助下民,为立君以政之,为立师以教之。
古文《泰誓》虽伪,但此语则不伪,因为《孟子·梁惠王下》早已征引过它了。又《国语·晋语一》也说:
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
可见在中国古代的一般观念中,君与师是同样重要的,政与教也是不容偏废的。汉代的循吏对于他们治下的“民”而言,便是既“作之君”而又“作之师”,既“食之”而又“教之”。详细的情况留待后面再说,现在让我们先讨论君师政教的分合问题。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史释》说:
“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其守官举职而不坠天工者,皆天下之师资也。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合于一,于是人之学术,不尽出于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而人乃狃于所习,转以秦人为非耳。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犹有合于古者,以吏为师也。
章学诚在这里对古代文化史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很有现代眼光的观察。他的主旨是说:三代时君师政教是合一的,春秋以后君师政教便分裂为二了。这个从合一到分裂的发展是无可置疑的。《庄子·天下》篇所说的“道术将为天下裂”便是对这一现象的确切的描述。不但中国古代有此突破性的发展,世界其他古文明也多经过这一突破的阶段。这也就是近来西方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所特别注意的“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 章学诚的深刻之处尤在于他已隐约地察觉到这一发展是带有必然性的。他在《原道上》说:
盖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气数之出于天者也。周公集治统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极,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圣人故欲如是以求异于前人,此道法之出于天者也。
此处所谓“天”即今语所谓“必然”或“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章氏指出“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也是合乎事实的。然而由于受到权威主义观点的限制,他似乎颇以秦人在这一方面“合于古”为可取。 他好像认为,如果“以吏为师”不限于“法律”,而同时也包括《诗》、《书》等儒家经典在内,那么秦制便无可訾议了。章氏在这一点上,显然陷于矛盾而不自知,因为根据他自己的历史判断,“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乃是“气数之出于天”和“事理之不得不然”。用现代的话说,在“哲学的突破”发生之后,文化系统和政治系统分化为二,各具相对的独立地位,从此便不能契合无间了。
秦人“以吏为师”在思想上渊源于法家的传统,从商鞅、韩非以至李斯都主张用政治系统来消解文化系统。所以商鞅先有“燔《诗》、《书》而明法令”之举(见《韩非子·和氏》篇),而韩非后来更明白地宣言: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秦始皇三十四年(西元前213年),丞相李斯的奏议提出“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即完全根据商、韩的理论而来。“以吏为师”至此更正式成为秦代的一个基本政策了。总之,在法家思想支配之下,不但“吏”与“师”、“政”与“教”合而为一,而且“师”从属于“吏”,“教”也完全由“政”出。这也许比三代的政教合一更为严厉。但是事实证明,政教既分之后已不是政治势力所能强使之重新合一的了。李斯奏议说:“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之制,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这句话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政教分途的实况。
秦代“以吏为师”的政策事实上是企图用政治秩序来取代文化秩序。这个政策在长程的历史发展中虽归于失败,但在当时则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从本文的观点说,我们必须指出,“以吏为师”使循吏的出现在事实上成为不可能。相反地,它却为酷吏提供了存在的根据。秦代守令之所以多流于残酷是和这一背景密切相关的。蒯通在秦末乱起之后对范阳令徐公说道:
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然则慈父孝子且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
秦吏只知有政治秩序,不知有文化秩序,所以对大传统中的基本价值如父慈子孝之类往往置之不顾。一旦政治秩序面临崩溃的危机,秦吏自然便首当其冲,成为人民报复的对象。《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元年”条云:
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
可见上引蒯通的话是丝毫没有夸张的。
人民之所以对秦吏普遍地不满,则是因为他们对于“吏道”另有一套看法而和秦廷的观点恰好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儒家仁爱教化的吏道观念长期以来早已在大传统中生根。秦代法令虽严苛,却始终不能把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从一般人的心中完全消灭掉。这是政教分立的必然结果。“教”提供了一个超越的支撑点(Archimedian Point),使人可以“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秦代的法令确曾在短期内有效地压制了文化的活力,使它几乎完全动弹不得。但是以儒教为主体的大传统仍然不绝如缕,最后还是随着秦代政治秩序的全面崩溃而重新获得生机。
秦代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吏道”观,分别地代表着“政”与“教”两个方面,这一点已由最近出土的秦代文献充分证实了。1975年湖北睡虎地十一号墓发现保存了大量的秦简,其中绝大部分是秦律,但有两件文献和本文的研究有特别密切的关系。第一件是《语书》,一般研究文学中往往称之为《南郡守文书》;第二件则是《为吏之道》。自发现以来,中外学者对这两个文件已有不少的讨论。本文不拟涉及其中种种枝节的考证。从本文的主旨出发,我们觉得这两个文件的性质恰好可以说明“政”、“教”两种“吏道”观点的分歧。
《语书》是官方文告,以南郡守腾的名义于始皇二十年(西元前227年)颁发给各县道的地方官吏。十一号墓主生前是地方小吏,故得保存一份。这个文告十足地体现了秦代“以法为教”的精神。它说:
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以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凡法律令者,以教道民,去其淫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也。
秦廷也重视“移风易俗”,但不是根据大传统的礼乐以推行“教化”,而是用政府所制订的“法律令”来“教导民”和“除其恶俗”。可见在秦代体制中“教”即由“法”出,此外并没有独立的源头。《语书》又说:
凡良吏明法律令,事无不能也……恶吏不明法律令。
这显然是以是否“明法律令”作为判别“良吏”与“恶吏”的第一标准。“良吏”必须“明法律令”,因为非如此他便不能执行“教导民”的任务。所以这篇文告完全证实了韩非所谓“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原则。韩非的理论其实也正是从秦代的实际政治经验中观察得来的。
《语书》所代表的是秦代官方对于“吏道”的观点,但是《为吏之道》的性质则迥然不同。它不是官方文书,而是私人编写的,其主旨在告诉人怎样才能做一个合标准的治民之“吏”。《为吏之道》在思想上的最大特色便是混合了儒、法、道各家的成分,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儒家思想还占据着主要的位置。例如“宽容忠信”、“惠以聚之,宽以拓之”等语,和上篇所引董仲舒“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的说法几乎先后如出一口。还有一些句子则十分接近汉代循吏的教化语言,如“除害兴利,慈爱万姓”以及“民之既教,上亦毋骄,熟导毋治(怠)”等皆其例。此中“除害兴利”四字在汉代常用在地方官的身上。《汉官解诂》(见孙星衍校集《汉官七种》本)且列“兴利除害”为“太守专郡”的正式职责之一。《为吏之道》也强调地方官的“师”的功能,故说:
凡戾人,表以身,民将望表以戾真。表若不正,民心将移,乃难亲。
“戾”作“帅”解,所以“戾人”即是“帅人”。这几句话显然是来自儒家的传统,与法家“以吏为师”之意大相径庭。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两相比较,《为吏之道》的话无疑即是《论语》的通俗化翻版。而且引文中的“表”字又与后来汉代常见的“良吏为民之表”的用法完全一致。《为吏之道》的作者同情于儒家关于“吏”的观点,因此也就连带地接受了儒家“治人”必先“修己”的前提。《为吏之道》开始第一节即说:
反赦其身,止欲去愿。
整理者注曰:“赦,疑读为索,反赦其身即反求于自己。”“止欲去愿”则注云:“遏止私欲。”这一理解是正确的。不过我们必须指出,这个“修己”的功夫是针对“吏”而发的,并不是要被治的人民反求诸己和遏止私欲。同节又有“正行修身”一语,这更明显是儒家的语言了。刘向《说苑》卷十《敬慎》篇云: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
又《汉书》卷四十四《淮南厉王传》载文帝令薄昭予厉王书,有云:
大王不思先帝之艰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
都恰可与“为吏之道”的“正行修身”互证,所以“为吏之道”确预设了儒家修、齐、治、平的实践程序。下面这一段话则集中地表现了“为吏之道”中的儒家观点:
术(怵)悐(惕)之心,不可不长。以此为人君则鬼(怀),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兹(慈),为人子则孝;能审行此,无官不治,无志不彻,为人上则明,为人下则圣(听),君鬼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志彻官治,上明下圣,治之纪也。
此段开端“怵惕之心”即指修养而言,上引《汉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可证。齐家、治国之道始于个人修养;君怀、臣忠、父慈、子孝也“一以贯之”。这和儒家“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之说大致是相通的。
和《语书》相对照,《为吏之道》所反映的显然是大传统中的吏道观。所以前者只强调以“法律令”为唯一根据的政治秩序,而后者则兼重“吏”的教化功能,在政治秩序之外还关心到文化秩序。总之,《为吏之道》保存了“政”、“教”分离以后的“教”的观点。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并未能完全截断儒家的教化思想伏流。由此可见汉代循吏观念的出现和发展自有其深远的文化背景,《为吏之道》便透露了此中的消息。
秦代“以吏为师”的政治秩序崩解以后,儒教因压力遽失而开始复苏。儒家强调政治秩序必须建立在文化秩序的基础之上,因此重“师”更过于重“吏”。根据这一观点,他们在讨论地方官的功能时,也往往把推行“教化”看得比执行“法令”更为重要。董仲舒在他的著名的对策中,一方面攻击秦代“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及由此而来的“好用酷之吏”,另一方面则主张设立太学以培养“教化之吏”。这便给循吏的出现提供了理论的根据。董仲舒说:
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过,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董仲舒从“教”的观点出发,所以强调“郡守、县令,民之师帅”,即以“师”为地方官的第一功能,“吏”的功能反而居于次要的地位。他把“教训于下”列在“用主上之法”之前,这正表示在他的观念中,文化秩序比政治秩序更为重要。事实上,通西汉一代,名臣奏议凡涉及吏治的问题几乎无不持儒家教化之说。对于只知奉行朝廷法令以控制人民的地方长吏,议者一概斥之为“俗吏”。让我们试举几个例子作为说明。
贾谊在著名的《陈政事疏》中说:
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为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
王先谦《汉书补注》此条下引周寿昌曰:
刀笔以治文书,筐箧以贮财币,言俗吏所务在科条征敛也。
周解甚确。“刀笔筐箧”的“俗吏”即是前文所引《兒宽传》所谓“文史法律之吏”。这种“俗吏”只知道如何去完成朝廷所交给他们的政治任务,如要求人民严守法纪和征敛赋税,但是对人民的生活则毫不关心。他们把执行“法令”看作自己在宦途上得意的唯一保证,因此往往不免流于严酷。“俗吏”和“酷吏”事实上是属于同一类的,不过程度有别而已。他们都是“循吏”的反面。循吏不但对于人民“先富之而后教之”,而且在“法令”和人民利益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他们甚至不惜违抗“法令”。上一节中兒宽“收租税时与民相假贷”和韩延寿“取官钱帛,私假徭役吏民”,便是两个具体的例证。
宣帝时王吉上疏也着重地指出:
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独设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凿,各取一切,权谲自在,故一变之后不可复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诈伪萌生,刑罚亡极,质朴日销,恩爱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礼之时,引先王礼宜于今者而用之。臣愿陛下承天心,发大业,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不若高宗?
元帝时匡衡上疏则说:
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
颜师古注末语曰:
非其天性自恶,由上失于教化耳。
王、匡二疏都一方面攻击“俗吏”仅恃“刑法”为维持政治秩序的工具,另一方面强调“礼义”、“教化”才是“治民”的根本。所以他们其实是主张用儒家型的“循吏”来取代汉廷所任用的“俗吏”或“酷吏”。
贾谊、董仲舒以来的大传统一直在强调郡守、县令必须首先发挥“师”的教化功能,而将执行“法令”的“吏”功能放在次要的位置。这是汉代循吏的思想渊源之所在。但是从制度史的观点说,汉代循吏以“教化”自任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汉廷并没有规定守、令有“教化”的任务。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只有“三老”才是真正“掌教化”的人。汉代诏令中,也只承认“三老”是“民之师”,而“三老”则与“孝弟”、“力田”等同是所谓“乡官”。他们是地方民众的代表,与“吏”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 汉承秦制,故严格言之,“吏”的本职仍然是奉行朝廷的法令。不过由于汉廷已公开接受儒教为官学,因此不得不默认地方官兼有“师”的功能而已。以下让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汉代守、令的本职在制度上确是执行“法令”之“吏”而不是推行“教化”之“师”。《汉书》卷八十三《薛宣传》记薛宣答吏职之问云:
吏道以法令为师,可问而知。及能与不能,自有资材,何可学也?
这里“吏道以法令为师”一语最能表示汉代的吏职仍然限于执行“法令”,与秦制是一脉相承的。礼乐教化根本不在吏的法定的权限之内。但是更明显的例子则是成帝时代的琅邪太守朱博。《汉书》卷八十三本传说:
博尤不爱诸生,所至郡辄罢去议曹,曰:“岂可复置谋曹邪!”文学儒吏时有奏记称说云云,博见谓曰:“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其折逆人如此。
朱博是“武吏”出身,似乎对儒生颇为反感,因此他的作风恰好是循吏的反面。罢除议曹便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说明。汉代郡守之有议曹,犹如皇帝之有谏大夫、议郎之类。循吏接受儒家的观念,以受言纳谏为美制,如上一节所讨论的韩延寿“所至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两汉书中有关议曹的记载不过三四处,但除上引《朱博传》中一条外,有两条都见于《循吏传》。 西汉宣帝时龚遂在皇帝召见前夕曾受议曹王生的教戒,他即据王生所教以陈对。 东汉初年任延拜会稽都尉,“会稽颇称多士。延到,皆聘请高行如董子仪、严子陵等,敬待以师友之礼。……吴有龙丘苌者隐居太末……乘辇诣府门,愿得先死备录。延辞让再三,遂署议曹祭酒。” 我们自不能据此极少数材料而断定循吏和议曹有什么特殊关联。但与“所至郡辄罢去议曹”相对照,则朱博的作风和循吏背道而驰是无可置疑的。议曹为散员,或置或罢皆可由地方长官个人决定,足证汉代郡守颇能自专。循吏的教化措施多是自出心裁,未必受朝廷指示,也由此益可见。
上引朱博答复文学儒吏的话则尤其重要,应略加分析。第一,他说:“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这句话可以看作汉代太守在法制上的正式定义。“三尺”指法律文书。《汉书》卷六十《杜周传》:“不循三尺法。”孟康注曰:“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居延汉简有一简是诏令目录,其长度适为汉三尺,尤为实证。 《杜周传》又说:“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所以“律令”统指历代皇帝所订之“法”。汉代太守的正式职务便是奉行这些“律令”,以维持政治秩序。朱博此语和薛宣所谓“吏道以法令为师”是完全一致的。第二,朱博拒绝听取文学儒吏向他讲“圣人道”,即是明白表示他不屑为“循吏”。文学儒生所称说的大抵不外礼乐教化之类的儒家观点,而他对于这一套则完全不感兴趣。因此他才以讥讽的口吻要他们把这种说辞留待“尧、舜之君”。汉代太守和属吏之间有“君臣之义”,故朱博此处以“君”自许。这一点后文还会提及,暂不多说。朱博的例子最能从反面说明,汉代循吏致力于文化秩序的建立完全出于自作主张。秦代之吏多“酷”,上文已加证明。汉代的政策放宽了一大步,对于地方官吏的统治方式大致采放任的态度,故吏之为“循”、为“酷”可由各人的思想和风格来决定。但汉廷对于“吏”的基本要求则仍是秦代的延续,即必须“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试想礼乐教化如果是出于朝廷的旨意,则朱博何敢如此理直气壮地拒斥“圣人之道”?朱博已是西汉末期的人物,哀帝建平二年(西元前5年)他在一个月之内先后拜御史大夫以至丞相。这时儒教表面上定于一尊已超过了一个世纪,然而像朱博这样一个鄙薄儒教的人竟能一帆风顺地攀登至官僚系统的顶峰。这一事实也迫使我们不能不重新思考汉廷和儒教之间的微妙关系。
薛宣和朱博关于“吏道”的界说大体上代表了官方的观点。但是另一方面,自西汉中叶以后,大传统中的吏道观也逐渐深入人心。《盐铁论·申韩第五十六》文学曰:
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贵良吏者,贵其绝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今之所谓良吏者,文察则以祸其民,强力则以厉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专己之残心,文诛假法以陷不辜、累无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
昭帝时盐铁争议,以御史大夫为首代表朝廷的观点,以贤良、文学代表民间大传统的观点。朝廷以律令为重,故御史大夫推重法家;大传统以儒教为根据,故文学开宗明义便说:“窃闻治人之道……广道德之端……而开仁义……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本议第一》) 上引文学之言,便列举了两种不同的“吏”:“绝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的“良吏”即是“兴教化、移风俗”的循吏;“文察”、“强力”型的“今之所谓良吏”则是朝廷所欣赏的酷吏,汉代两种吏道观的对比在《盐铁论》中是表现得非常清楚的。
以“教化”代替“刑杀”是汉代儒士的共同要求,上起西汉的贾谊、董仲舒,下至东汉的王符无不反复言之。 因此在一般的社会观念中,“吏道”绝非如薛宣所云,只是“以法令为师”。相反地,儒教经典在“吏道”中所占的分量远比律令为重。这一点在西汉晚期的一部小学教科书中有极清楚的反映。《急就篇》说:
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治礼掌故砥砺身,智能通达多见闻。
《急就篇》相传出自元帝时代(西元前48~前33年在位)史游之手,是一部流传极广的字书。在西汉末叶,《急就篇》已传到了边疆,敦煌和居延出土的汉简中都有此书的残简。 所以此书颇能反映当时人的一般观念。上文所引有关“宦学”一节便是大传统中吏道观的具体说明。“宦学”即是“吏学”的同义语,其必读之书首先是儒家经典。第一句之《论》乃《论语》的简称,如《鲁论》、《齐论》、《古论》之例。成帝时张禹精于《论语》,他整理的本子号为《张侯论》。《汉书》卷八十一本传载当时流行语“欲为《论》,念张文”,尤为《论》即《论语》之证。《急就篇》论“宦学”先列《诗经》、《孝经》与《论语》三书是饶有深意的。因为《诗经》在汉代是“谏书”,即儒生持“道”以议“政”的一部宝典,而《孝经》、《论语》则是教化思想的总汇。汉儒向朝廷敷陈“德治”往往引此二书之文为立说的根据。《春秋》在汉代被公认为孔子所自著之书,《尚书》则是古史,何以在《急就篇》中反而与“律令文”并列呢?这是因为这两部书早已被朝廷用来“断狱”,具有法律的性质了。《史记·酷吏列传·张汤》说:
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
可见《急就篇》此节列举书名次第经仔细斟酌,绝非漫无标准。“德治”在前,“刑治”在后,“律令文”在宦学必读书中则居末位。这一安排正如实地反映了大传统中的吏道观。此节第三句中的“砥砺身”即指“修身”而言,也是汉代儒吏的常用语。《汉书》卷七十六《王尊传》“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厉,助太守为治”可以为证。“修身”是大传统中吏道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自孔子以来流衍不绝,前引秦简《为吏之道》中也有其说。《急就篇》虽是一部启蒙的字书,其中却保存了汉代吏学的具体内容,其史料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总结地说,汉代一直存在着两个关于“吏道”的不同观点:一个是朝廷的观点,上承秦代而来,所以“吏”的主要功能只能是奉行“律令”;另一个是大传统的观点,强调“化民成俗”为“吏”的更重要的任务,奉行“律令”仅在其次。在思想上,前一观点与法家的关系很深,并为“酷吏”或“俗吏”的行为提供了理论的根据。后一观点则渊源于儒教,“循吏”的礼乐教化论即由此而起。这两个观点当然不是完全对立的,但取向(orientation) 确有不同:前者可称之为“吏”的取向,后者则不妨名之为“师”的取向。这分野几乎在汉代一切文献中都可以获得印证,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六)循吏与文化传播
汉代循吏在文化传播方面的活动,两汉书《循吏传》记之甚详,此外其他传记和碑铭中也随处可见。本文不能详引一切有关史料以说明循吏的具体教化过程,因为那样做便会流为一部“汉代循吏资料汇编”了。本节只能采取提要钩玄的方式,运用一个整体的观念来阐释循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不用说,正史和碑文中的记载自不免有溢美的严重问题。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下,我们都没有异源的史料足以与碑传文字互相参证。因此个别的事迹是否都真实可信,我们无从判断。但本文所研究的是把循吏作为一种典型人物的活动方式,就这一点言,我们的证据是极其充足的。以下征引史料仅取其中所透露的一般性的活动方式,个别事迹的真实性只好存而不论。不容讳言,中国史学的语言一向笼罩在一层道德判断的浓雾之中,但现代的读者并不难透过这层浓雾去认识客观的历史面目。
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汉代循吏的治民内容和方式都与儒家的原始教义是一致的。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循吏的推行教化确是出于自觉地实践儒家的文化理想——建立礼治或德治的秩序。因此,个别循吏的活动虽因时因地而各有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都合乎儒家、特别是孔子的基本教义。现在我们必须证实这一推断。
五十年前,政治学者张纯明曾以英文发表了一篇研究循吏的专著。这篇专著是通论中国史上自汉至清的循吏的。他分析正史中的《循吏传》,指出他们的成就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一、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二、教育;三、理讼。张氏特别注意到教育一项的重要性。他所说的教育则指两个方面:一是正式的学校教育,如文翁之立郡学;一是社会教育,即对于一般人民的礼乐教化。他并且强调地说:循吏如果仅仅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而不同时对他们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也加以改进的话,那么他便不成其为第一流的循吏了。
张氏此文是纯从现代地方行政的观点立论的,他并没有讨论到循吏的文化意义。他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循吏和孔子以来的儒教有任何历史的关系。但正因如此,这篇文字才特别值得一提,因为它的作者丝毫没有儒家的成见,但它所作的纯现象论的描述最后竟和儒家教义不谋而合。读者不难发现,此文所归纳出来的三大特征正是孔子所重视的“富之”、“教之”和“无讼”。这可以旁证我们关于循吏有意识地推行儒教的推断。以下让我们举例稍作说明。
《汉书·循吏召信臣传》: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寿春人也;以明经甲科为郎,出补谷阳长,举高第,迁上蔡长。其治视民如子,所居见称述……迁南阳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府县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为事,辄斥罢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视好恶。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曰召父。
《后汉书》卷四十三《何敞传》云:
岁余,迁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当时名誉,故在职以宽和为政。立春日,常召督邮还府,分遣儒术大吏案行属县,显孝悌有义行者。及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百姓化其恩礼。其出居者,皆归养其父母,追行丧服,推财相让者二百许人。(注引《东观记》曰:“高谭等百八十五人推财相让。”)置立礼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鲖阳旧渠,百姓赖其利,垦田增三万余顷。吏人共刻石,颂敞功德。
召信臣是西汉元帝时人,何敞则大约卒于东汉安帝之世(107~125),相去一百余年,但两人的治民内容和方式大致相同。例如富民、教民和理讼三项始终构成循吏活动的主要特色。何敞不在《循吏传》中,正如西汉的韩延寿。但他是一个典型的循吏则毫无问题。此处特别引他为例,以见研究汉代循吏决不应以两汉书的《循吏传》为限。如果仅据《循吏传》中少数例子来分别两汉循吏的前后不同,则不免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汉书·循吏传序》特别强调循吏“所居民富”的特色,我们必须对这一点稍加分析。在循吏的“富民”活动中,自然以水利灌溉和农田开拓最为重要。前已引西汉文翁、召信臣之例。东汉以下这一类的记载更多至不胜举,下面是几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例子。
杜诗,建武七年(31年)迁南阳太守,“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时人方于召信臣,故南阳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这个例子的重要性在于它说明了两汉循吏“富民”工作的延续不断。据《水经注》 ,南阳水利“汉末毁废,遂不修理”。但郦道元又接着说太康三年(282年)杜预“复更开广,利加于民。今废不修矣”。《水经注》记召信臣的水利工程始于建昭五年(西元前34年),则前后持续了三个世纪以上。
王景,建初八年(83年)迁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注:陂在今寿州安丰县东),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半给。遂铭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庐江传其文辞。” 我们特别介绍王景在庐江的水利,不仅因为他是中国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师,而且更因为他的闸坝工程遗址最近已在安徽寿县安丰塘发现了。
张导,建和三年(149年)为巨鹿太守。“漳津泛滥,土不稼穑。导披按地图,与丞彭参、掾马道嵩等原其逆顺,揆其表里,修防排通正水路。功绩有成,民用嘉赖。”
王宠,《水经注》卷十一“沔水”条记木里沟为汉南郡太守王宠所凿,“故渠引鄢水,灌田七百顷,白起渠溉三千顷。膏粱肥美,更为沃壤也”(页二一) 。
以上两条见于《水经注》,是郦道元在5世纪末期调查所得。张导一条即据当时尚存之碑文。我们相信这几处的记载都近于实录,证明汉代循吏在水利灌溉方面确有贡献。
上引《王景传》中记王景教人民犁耕和蚕织,这也是循吏“富民”工作中常见的部分。《后汉书·循吏列传》中还有任延东汉初出任九真太守,“九真(按:今越南河内、顺化一带)……不知牛耕,民……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有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柘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李贤注引《东观记》说:“建武中,桂阳太守茨充教人种桑蚕,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颇知桑蚕织履,皆充之化也。”九真、桂阳在当时都是边境,循吏把较高的经济技术推广到这些地方是很可能的,虽然记述之词难免夸张之嫌。让我们再引《循吏列传》以外的一个例子。《后汉书》卷五十二《崔寔传》云:
出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纴、綀缊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
现存《四民月令》相传出自崔寔,也许是可信的。所以他能教五原人民种麻和织绩,毫不足异。崔寔可以说是循吏世家,他的父亲崔瑗,顺帝时(125~144)曾任汲县县令,为民“开稻田数百顷。视事七年,百姓歌之”(同上本传) 。更值得注意的是崔寔的母亲刘氏,《崔寔传》说:
母有母仪淑德,博览书传。初,寔在五原,常训以临民之政,寔之善绩,母有其助焉。
这个故事使我们联想到前引酷吏严延年的母亲所说“仁爱教化”的话。循吏教化的观念在汉代大传统中植根之深,即此可见。
我们也必须指出,汉代地方官的考绩中包括户口和垦田的增加,这是所谓“兴利”的主要部分。人口和田亩的数量是和政府所得的赋役成正比例的,因此完全符合汉廷的劝农政策。 当时地方官甚至有虚报田亩的现象。《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般传》载永平十一年(68年)刘般上言有云:
又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故诏敕区种,增进顷亩,以为民也。而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可申敕刺吏二千石,务令实核,其有增加,皆使与夺田同罪。
即是明证。所以我们决不能把所有兴水利灌溉及鼓励农桑的地方官都一律看成实行儒家教化的循吏。事实上,酷吏也有“教民耕田种树理家之术” 的。而且地方官兴水利的传统由来已久,早起于战国之世,魏文侯时代的邺令西门豹和秦昭王时代的蜀守李冰都是著名的先例。 但我们在前面所举的例证则显然不能和普通地方官执行政府法律的情况相提并论。他们的功绩在数百年之后尚为当地人民所怀念,则其间必贯注了不少心力。而且循吏的“富民”也不限于水利农田,他们对于商业也同样加以保护。我们也举两个例子。《后汉书·循吏孟尝传》记孟尝为合浦太守事云:
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以病自上,被征当还,吏民攀车请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遁去。隐处穷泽,身自耕佣。邻县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
这是有名的“合浦还珠”的故事,《水经注》(卷十四,页一一)也记载孟尝为守,“有惠化,去珠复还”。第二个例子见于《桂阳太守周憬功勋碑》(收在《全后汉文》卷一○三)。此碑立于熹平三年(174年)三月,原文甚长,又多有缺字,不能详引。大旨是称述周憬疏凿水道之功。碑文说桂阳与“南海接比,商旅所臻”,但水路极险,舟行困难。周憬既“伤行旅之悲穷,哀舟人困厄”,于是效法蜀守李冰的故事,命良吏率壮夫加以治理。最后大功告成,“抱布贸丝,交易而至”,“船人叹于水渚,行旅语于途陆”,这两处的记载在文字层面或不免夸张,但其中所透露的基本事实则是不容置疑的。
循吏的特色不仅是“富民”,而尤在于“先富而后教”,前引召信臣、何敞两例已足以为证。现在让我们再举一例以说明循吏的“先富后教”确是自觉地实践孔子之言。《三国志》卷十六《杜畿传》记杜畿在建安时(196~220)任河东太守事曰:
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少耗减。畿治之,崇宽惠,与民无为。民尝辞讼,有相告者,畿亲见为陈大义,遣令归谛思之,若意有所不尽,更来诣府。乡邑父老自相责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从其教?”自是少有辞讼。班下属县,举孝子、贞妇、顺孙,复其徭役,随时慰勉之。渐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农,家家丰实。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
裴松之注引《魏略》曰:
博士乐详,由畿而升。至今河东特多儒者,则畿之由矣。
杜畿在河东的表现足以当循吏的典型而无愧。他不但尽力实行孔子“导德齐礼”和“必也使无讼”(《论语·颜渊》)的理想,而且明确地表示他的行动根据是来自《论语》的“既富矣,教之”。至于他亲自执经教授的成绩则又有《魏略》为之证实。所以杜畿的例子集中地显露了汉代循吏的特色,特别是在“师”重于“吏”这一点上。
西汉末期以来,由于儒教已深入社会,循吏之中颇有人更自觉到“师”是他们的主要功能,因此地方官亲自与生徒讲学之事也更为普遍。上引杜畿“亲自执经教授”便是在这一风气下所形成的。《后汉书·儒林列传·牟长》记他建武初年任河内太守云:
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著《尚书章句》,皆本之欧阳氏,俗号为《牟氏章句》。
同书《儒林列传·伏恭》记他建武时:
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
牟、伏两人名列《儒林传》,可见身后定论他们都是经师。但他们讲经学竟都在太守任内,这可以看出汉代儒吏虽一身兼具“吏”与“师”两重身份,但二者并未合一。对于牟、伏两人而言,他们的最后认定更显然在“师”而不在“吏”。同书卷二十五《鲁丕传》:
元和元年(84年)征,再拜赵相。门生就学者常百余人。关东号之曰:五经复兴鲁叔陵。
则鲁丕也有资格和牟、伏同入《儒林传》。同书同卷《刘宽传》记他在桓帝时,
典历三郡,温仁多恕,虽在仓卒,未尝疾言遽色。常以为:齐之刑,民免而无耻。吏人有过,但用蒲鞭罚之,示辱而已,终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灾异或见,引躬克责。每行县止息亭传,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人感德兴行,日有所化。
刘宽也是一个典型的循吏。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本传引华峤《后汉书》云:“为南阳太守,教民种柘、养蚕、织履,生民之利。”可见他的治民方针也是“先富后教”。不过他的“教”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部分:一方面他以“经师”的身份与学官诸生讲经,另一方面他又以“教化之师”的身份对民间父老子弟宣扬大传统中的道德观念。刘宽熹平五年(176年)为太尉,故洪适《隶释》十一有“太尉刘宽后碑”。这个碑便是他的门生颍川殷苞等“共所兴之”的。由此可知他的“师”的身份比“吏”更受重视。
以上都是郡守一级的循吏,下面再举几个县令长的例子。《后汉书·文苑下·刘梁传》说:
桓帝时,举孝廉,除北新长。告县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汉,庚桑琐隶,风移碨磥。吾虽小宰,犹有社稷,苟赴期会,理文墨,岂本志乎!”乃更大作讲舍,延聚生徒数百人,朝夕自往劝诫,身执经卷,试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后犹称其教焉。
刘梁的例子最能说明汉代循吏对于“吏”、“师”之分的自觉。“赴期会,理文墨”,只是发挥“吏”的功能,这是他所不能满足的。因此他把主要的精神放在聚徒讲学上面。他在“吏”与“师”之间的抉择是非常清楚的。光和六年(183年)所立的《汉成阳令唐扶颂》(《全后汉文》卷一○四)有云:
抠衣受业,著录千人。朝益暮习,衎衎訚訚。尼父授鲁,何以复加?
这里颂扬的正是县令唐扶的兴学授徒。弟子著录先后至有千人之多,则学校规模可想而知。县令讲学的风气下及三国时代仍然存在。《水经注》卷十二“沔水”阴县条下云:
县东有县令济南刘熹,字德怡,魏时宰县,雅好博古。学教立碑,载生徒百有余人,不终业而夭者,因葬其地,号曰:生坟。(页二)
东汉循吏颇多县令长一级的人物。《后汉书·循吏列传序》曰:
自章、和以后,其有善绩者往往不绝。如鲁恭、吴祐、刘宽及颍川四长(李贤注:谓荀淑为当涂长,韩韶为嬴长,陈寔为太丘长,钟皓为林虑长。淑等皆颍川人也),并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
此所举七人之中,除吴祐、刘宽以外,都是县令长。此外尚有雍丘令刘矩和东平陵令刘宠(均见《后汉书·循吏列传》)也都是有名的循吏。又有西汉末年密令卓茂,在东汉初特别受到表扬(《后汉书》卷二十五) 。卓茂和鲁恭两人更是所谓“死见奉祀”的典型,其祠至5世纪末尚存在,分见《水经注》卷九“洧水”及“水”。不但郡守、县令长推行教化,甚至亭长也有化民成俗的事。《后汉书·循吏列传·仇览》:
仇览字季智,一名香……为蒲亭长。劝人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豕有数。农事既毕,乃令子弟群居,还就黉学。其剽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严设科罚。躬助丧事,赈恤穷寡。期年称大化。览初到亭,人有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元不孝。览惊曰:“吾近日过舍,庐落整顿,耕耘以时。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养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义乎?”母闻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乡邑为之谚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鸤枭哺所生。”
仇览后来在太学时为郭林宗所赏识,故他的事迹流传甚广,颇有异词。如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说览“责元以子道,与一卷《孝经》,使诵读之”。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三“建宁三年”(170年)条并详引仇香(即览)告陈元母之语。但其人其事的大体应无可疑。《后汉书》中的循吏颇多县令长一级的人物是一个值得注目的现象,它似乎显示儒教大传统确实逐渐渗透到民间日常生活之中。《汉书》中也有朱邑为桐乡啬夫和召信臣为上蔡长,并在这些较低级的职位上表现了循吏的特色,但他们最后的成就仍然是在郡守的任上(见《循吏传》)。西汉末年以来的循吏则多有在县令任上即完成其教化任务者,如卓茂、鲁恭、颍川四长、刘矩、刘梁等都是显例。仇览的教化成绩且仅止于亭长之任,因为他自太学卒业之后便拒绝出仕了。总之,《后汉书》中的循吏人数远多于《汉书》(不限于《循吏传》),而且县令级循吏的大量出现更是一个明显的特色。这一历史记载上的差异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实际的变化,使我们具体地看到在儒教社会化的过程中两汉循吏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循吏不但逐步把大传统注入民间,而且也曾努力将中原的生活方式传播到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的社会,因而不断地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范围。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举一二例稍作说明。据《后汉书·循吏卫飒传》,他在建武初年迁桂阳太守:
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
这个记载显然过分夸大了卫飒的教化效果,但他曾在桂阳从事教化的努力大概是可信的。同书《任延传》更为重要,传云:
建武初……诏征为九真太守。光武引见,赐马、杂缯,令妻子留洛阳。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聘,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徼外蛮夷夜郎等慕义保塞,延遂止罢侦候戍卒。初,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
不用说,这一记载中颇有渲染和汉民族的偏见,但是其中也有可以辨识的基本史实。例如光武令任延的妻子留洛阳,《后汉书》并无解释。其实这是汉代的“质任”制度。据《三国志》卷二十四《王观传》,凡郡为“外剧”则太守须有任子。时王观为涿郡太守,为了降低人民差役的等级,自动定涿郡为“外剧”,“后送任子诣邺” 。九真在东汉初当是“外剧”,所以光武帝要留任延的妻子在洛阳为人质。证实了这一点,我们便可相信此事的大体轮廓是真实的。任延在九真所推行的即是一般循吏的“先富后教”政策,毫不足异。他大概也和卫飒一样,曾在九真“设婚姻之礼”,至于骆越之民是否“无嫁娶礼法”,或有其法但与汉民族不同,我们只好存疑。关于效果方面的描写,原文无疑是夸张得过度了。不过我们确有理由相信“岭南华风”始于锡光、任延两人的教化。《三国志》卷五十三《薛综传》载综上疏孙权论交州事有云:
及后锡光为交,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于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由此已降,四百余年,颇有似类。
据《薛综传》,综曾任合浦、交太守,又随吕岱越海南征,亲到九真。所以他的话是本之实地考察,自较可信。他在疏中只说“颇有似类”,语极平实,也无夸大之嫌。要而言之,我们固不能轻信儒教具有史书上所渲染的那种“化民成俗”的神奇力量,但是事实俱在,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循吏的教化确有助于儒教的传播。南方在中国史上的逐渐“儒教化”便是一个有力的见证。 任延后来又出任武威太守,他也同样在河西地区推行一贯的教化工作。本传说:
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孙皆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由于《后汉书·循吏列传序》中有“移变边俗”之语,因此有人以为这是东汉循吏的特色所在。 但是从本篇所引东汉循吏的活动来看,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内地的循吏事实上仍然比边郡为多。而且西汉循吏也未尝不以“移变边俗”为己任,如最早的文翁在蜀郡推行教化便是因为“蜀地僻陋,有蛮夷风”。东汉边郡的循吏比西汉为多,大致可归于两个原因:第一是西汉末叶以来循吏的总人数逐渐在增加。由于儒教的影响日益扩大,为吏者人人都以争做循吏为荣。二世纪初班固《汉书》开始流传,西汉循吏的事迹更发生了示范的作用,“循吏”一词也成为对地方官的最高礼赞。例如熹平二年(173年)所立的“汉故司隶校尉忠惠父鲁君碑”便说:
迁九江太守。……行循吏之道。统政口载,穆若清风,有黄霸、召信臣在颍南之歌。
这种颂词似乎是受了《汉书·循吏传》的影响。熹平是灵帝年号,服虔、应劭为《汉书》注音义即在这个时期。循吏的总人数既增,边郡自然也相应而出现较多的教化活动。第二个原因是两汉的边郡情况颇有不同。东汉的政策是尽量把“内属”的少数民族包括在帝国的境内,并尽可能地置他们于郡县系统之内。例如凉州汉人与羌人杂处的情况早在东汉初年便已极为严重。这也是东汉何以特别有“移变边俗”的问题。
汉代循吏虽是大传统的“教化之师”,然而这并不表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用大传统来取代各地的小传统,或以上层文化来消灭通俗文化。我们在上篇已指出,中国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或上层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是互相开放的,因而彼此都受对方的影响而有所变化。其结果是一方面大传统逐渐在民间扩散其移风易俗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小传统中的某些成分也进入了大传统,使它无法保持其本来面目。现在让我们以循吏为例对这一情况作一点具体的解说。《后汉书·循吏列传·王景》说:
初,景以为《六经》所载,皆有卜筮,作事举止,质于蓍龟,而众书错糅,吉凶相反,乃参纪众家数术文书,冢宅禁忌,堪舆日相之属,适于事用者,集为《大衍玄基》云。
从现代的眼光看,王景的《大衍玄基》竟可说是一部集迷信之大成的书。即使在东汉,王充《论衡》中《四讳》、《时》、《讥日》、《卜筮》、《辨祟》等篇便已针对这些迷信而发。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怀疑循吏的“移风易俗”的功能呢?首先我们愿意指出,循吏如王景对于世俗迷信的注意和王充的批评恰好可以看作汉代大、小传统互相沟通的证据。以王充而言,他曾屡为州、郡、县的属吏(功曹掾、州从事、治中等),注意民间各种禁忌,并搜集一切有关的记载。因此《论衡》中才保存了大量的汉代风俗信仰。此外他还写了《讥俗》和《政务》两书(据《自纪》篇),也都与他的地方吏职有关。他写这一方面的文字正是出于“移风易俗”的动机,故曰:“《讥俗》之书,欲悟俗人。”(《自纪》) 从王充的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到汉代小传统中禁忌之多及其入人之深。郡县守令如果不注意这些民间的风俗信仰,便根本不能和人民之间发生任何沟通了。王景的《大衍玄基》特别重视“适于事用者”,大概便是一种因势利导的工作。风俗信仰之事是不可能用政治强力来加以禁绝的,循吏所能做的不过是禁止其中对人民生活极端有害的部分。至于那些无伤大雅的部分也只好采用董仲舒所谓“宽制以容众”的办法。而且循吏既不能完全不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大传统也不能免于小传统的侵蚀。汉代阴阳五行的观念弥漫于整个儒家经典之中,《易经》尤其如此。王景早年即专治《易》,再看其书名及本传“以为《六经》所载,皆有卜筮”之语,即可知他是想以他所理解的大传统来改造民间的小传统。甚至王充也未能完全免俗,《论衡》驳斥世俗忌讳,最后往往折中于儒家经典。他也接受当时通俗文化中的某些信仰,如土龙求雨、服药导引之类,不过予以较近于常识的解释而已。 让我们再举一证,以澄清大、小传统的关系。《后汉书》卷六十五《张奂传》:
(延熹六年,163年)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赋,率厉散败,常为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产子及与父母同月生者,悉杀之。奂示以义方,严加赏罚,风俗遂改,百姓生为立祠。
张奂在武威的作风也足当循吏之称,而他所改的风俗则见于《论衡·四讳》篇之第四讳,即“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其中“二月”与“正月”之异,不知是否是《后汉书》辗转传抄有误。(王充所记乃“正月”,则由下文可定,绝不会错。) 但传末又说:
初,奂为武威太守,其妻怀孕,梦带奂印绶登楼而歌。讯之占者,曰:“必将生男,复临兹邦,命终此楼。”既而生子猛……卒如占云。
可见至少张奂之妻信“占”,与世俗不异。但这两种不同的“迷信”则决不可同日而语,前者直接引起杀婴的社会问题,后者则无论验与不验都没有严重的后果。循吏以建立和维持一个稳定而健全的文化秩序为第一要务,因此对前者自不能不严禁,对后者则不妨随俗。事实上以占卜为“迷信”是现代人的观念,汉代人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则并未有此想法。王充在《卜筮》篇也说“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误也”,又说“盖兆数无不然;而吉凶失实者,占不巧工也”。其他汉代大传统中人信占卜者更比比皆是,《白虎通·蓍龟》篇、《潜夫论·卜列》篇皆可作证,何况占卜星相之类的民间信仰一直到今天仍或多或少流行在每一文化之中。所以研究通俗文化史尤其不能以“科学”为借口而持一种非历史的态度。上引王景、张奂之例,从文化史的观点看,正足以说明汉代循吏在沟通大、小传统方面所产生的作用。
最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则是近数十年来秦汉简牍的发现为汉代大、小传统的关系提供了绝好的证据。1959年甘肃武威县磨嘴子六号汉墓出土了大批木、竹简,其中最重要的是《仪礼》四百六十九简。此外还有日忌、杂占木简十一枚。据推测,墓主大概是武威郡学官中的经师,死在王莽时代。《武威汉简》的编者考证此十一简云:
敦煌、酒泉、居延等汉代烽燧遗址所出木简,多为屯戍文书,亦间有少数典籍、律令、历谱、医方并占书、日禁之书等。汉俗于日辰多忌讳,又信占验之术,王充讥之。(中引《张奂传》从略)不信民间之忌而信占验之术,此所以此墓主虽为饱学经师而于日禁之书有死生不能忘者,故与所习儒书同殉焉。
又说:
日忌简则综列诸事于日辰之下,编以韵语,乃民间书也。《论衡·辨祟》篇所举汉俗避日者有起功、移徙、祭祀、丧葬、行作、入官、嫁娶等事,而日忌简所举有治宅、纳财、置衣、渡海、射侯及盖屋、饮药、裁衣、召客、纳畜、纳妇等事。
武威汉墓中礼禁和日禁之书同殉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若持以与王景、张奂事相参证,更可见汉代大、小传统之间有一种并行不悖的关系。武威的日忌究竟是反映了墓主个人的信仰,还是和他生前的职务有关,今已不能确定。汉俗日忌如上引简文所举者都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有关,所以地方长官及其属吏对此不能不加以密切的注意,王充便是以属吏而搜集卜筮、日忌之书的例子。《武威汉简》的编者推测其主人可能是“礼掾”之类,除据《仪礼》、《丧服》简外,主要是因为日忌木简背后有“诸文学弟子”一语。这一推测自甚合理。但此简是河平年间所书,下距其卒尚有数十年。故编者又说:“自河平中至其卒年,其官秩应有所改变。”假定他后来转任郡属吏如功曹、主簿之类,则日忌简便和他的职务有关了。 我们之所以如此推测是因为受到云梦秦简的启示。简的主人喜是与法律有关的地方小吏(安陆令史、鄢令史) ,所殉之简大致有三类:法律文书(包括《语书》) 、《为吏之道》和《日书》等卜筮日忌之书。前两项都和死者生前的职务有关,《日书》似不应单独反映死者的信仰。而且何以秦末和西汉末两个死者恰好不约而同地都以日忌之书殉葬?秦汉民间各种信仰甚多,又何以两人都特别选上日忌一种?如果此一推测不误,那么前文论秦代地方官已与移风易俗有关,便更是信而有征了。西汉中叶以后,循吏越来越以“师”自居,视“教化”为治民的首务,他们之终于成为大、小传统的中介人物,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归趋。
(七)循吏与条教
最后,我们必须讨论一下汉代循吏何以能自出心裁以推行教化的问题。从较大的历史背景来说,我们首先自然要考虑到社会经济的一般状况。汉代是中国史上第一个获得长治久安的统一王朝,无论是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都处于历史转型的时期。以社会言,汉代正在从古代封建贵族体制蜕变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体制;以经济言,农业和商业也是处在上升发展的新阶段。汉代循吏因此有较多的活动余地,可以从事于“富民”、“教民”的努力。这是后世地方官吏所缺乏的有利条件。但是这一社会经济的背景牵涉的问题甚广,此处无法详说,只可点到为止。
其次,较为具体的是政治制度的背景。秦汉的郡县制代古代的封建制而起,直接统属于中央政府,但另一方面,郡县守令也继承了封建王侯独揽一方的大权。哀帝时王嘉上疏说:
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
武帝时严安上书说得更为严重:
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畿千里非特闾巷之资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万世之变,则不可胜讳也。
这是说郡守集地方的政权、财权和军权于一手,遇到变乱的机会是可以背叛朝廷的。严安的话并非夸张,汉代郡守确于一郡政务无所不统,是一元首性的地方长官。甚至县令长的治县之权也是既专且重。关于制度方面的实际情况,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秦汉部分有十分详尽的研究。我们现在则要进一步说明汉代循吏怎样运用这种庞大的权力来推行教化。所以本节特别提出“条教”的观念来作一检讨。
“条教”这个名词虽然是读汉史的人都熟悉的,但其确切含义则仍待澄清。《汉书》卷八十三《薛宣传》:
出为临淮太守,政教大行。
《三国志》卷七《臧洪传》广陵太守张超之兄邈谓超曰:
闻弟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
汉代郡守以政、教连言,以上不过聊举两则示例而已。“政”指朝廷政令,但“教”是何义?《资治通鉴》卷一六六《梁纪》二十二敬帝太平元年(556年) 十二月周迪为衡州刺史,“政教严明”下胡注曰:
教,谓教令,州郡下令谓之教。
(按:胡注甚确。)《风俗通义》卷四《过誉》记:
司空颍川韩,少时为郡主簿,太守葛兴被风病,恍忽误乱,阴辅其政,出入二年,置教令无愆失。
可证“教”是郡守所出之“令”,也可称“教令”。胡注稍需补充者,《三国志》卷五十五《黄盖传》记盖出长石城县,向县吏下令,有“教曰”云云,可知县令长下令也可称“教”,不止胡注所言州郡。
“教”的意义既明,则“条教”必与之相关。我们可以推测“条教”大概便是地方长官所颁布的教令而分条列举者。《汉书》用“条教”两字最早似见于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
董仲舒曾先后为江都、胶西相,本传明说他“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可见他所著“条教”若干篇必是在国相任内所出的教令,因为其教令是出之以条列的方式,故称为“条教”。董仲舒的“条教”不传,我们无从知其内容。汉代较早而又清楚的“条教”见于《汉书·循吏黄霸传》。传云:
霸为颍川太守……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米盐靡密,初若烦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
传文自“条教”以下都是描写其“教”的内容。原“教”当是条分缕析,所以称之为“烦碎”。黄霸的“条教”显然是名副其实的“教化”,不出“富之”、“教之”的范围。我们已不能确定郡县守令下“令”为什么要称之为“教”,也不知道这一习惯始于何时。但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用法则是文翁。本传说:
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閤。
其次是董仲舒,已见上文。这两人都是景、武时代的儒家,并提倡“教化”最力。而且最先以“政”、“教”并举的是孟子。《孟子·尽心上》:
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的话又是发挥孔子的观念。《论语·为政》: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论语》此节末句,汉代人常常引用,断句作“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清代周寿昌已指出,见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二十五《卓茂传》。所以我们可以推断汉代郡守下令曰“教”或许渊源于儒教。当然我们也不敢断然否定它完全与韩非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无关。不过以汉代“政”、“教”并举的情形来说,这一用法至少是更接近孟子的。
“条教”的较早的用法也恰好和儒家背景的守、相有关,如上引董仲舒、黄霸之例。下面让我们再举几个循吏型的“条教”。《汉书》卷七十九《冯立传》:
立……迁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职公廉,治行略与(冯)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贷,好为条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为太守,歌之曰:“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知惠吏民,政如鲁、卫德化钧,周公、康叔犹二君。”
冯氏兄弟都是循吏,歌中“因循”两字即是循吏之“循”的原始义。此两人所立的“条教”大概也是属于“先富后教”的一类,否则何来“鲁、卫德化”之颂?同书卷八十三《薛宣传》:
宣……所居皆有条教可纪,多仁恕爱利。
《后汉书》卷二十七《张湛传》:
建武初,为左冯翊。在郡修典礼,设条教,政化大行。
同书《党锢李膺传》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
出补蜀郡太守,修庠序,设条教,明法令,恩威并行,蜀之珍玩不入于门。益州纪其政化。
另有不名为“条教”而实则相同者。同书《循吏童恢传》:
除不其令,吏人有犯违禁法,辄随方晓示。若吏称其职,人行善事者,皆赐以酒肴之礼以劝励之。耕织种收,皆有条章,一境清静。
童恢所实行的正是孔子“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之教。《后汉书集解》引《齐民要术》云:
恢为不其令,率民养一猪,雌雄鸡四头,以供祭祀、买棺木。
可见他的“条章”正和黄霸的“条教”相同,包括“畜养”在内。同卷《循吏仇览传》中也说:
劝人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豕有数。
这个“科令”也是一种“条教”。不知是否因为这两个人一是县令,一是亭长,所以才不用“条教”。
但是我们决不能说凡设“条教”者都是推行儒家教化的循吏。同书卷六十四《史弼传》李贤注引《续汉书》:
(弼父)敞为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条教,见称于三辅也。
我们并不能仅据“化有能名”四字便断定史敞是循吏,因为《史弼传》明说“父敞,顺帝时以佞辩至尚书、郡守”。还有明是酷吏型的郡守也善于“条教”的。《汉书》卷六十六《郑弘传》:
郑弘……兄昌、字次卿,亦好学,皆明经,通法律、政事。次卿为太原、涿郡太守,弘为南阳太守,皆著治迹,条教、法度为后所述。次卿用刑罚深,不如弘平。
同书卷七十六班固赞曰:
张敞……缘饰儒雅,刑罚必行,纵赦有度,条教可观。
《后汉书·酷吏周传》:
迁齐相,亦颇严酷,专任刑法,而善为辞案、条教。
从上引有关“条教”的资料中,我们看到,虽然“条教”似乎和儒家的教化有较密切的关系,但事实上汉代郡守、县令长,无论其政治倾向是儒是法,都可以在他们的治境之内设“条教”。每一套“条教”都代表一个地方官在他任内的政治措施,这种措施之所以称为“条教”,则是因为它是以分条列举的方式著之于文字的。所以“条教”对于每一郡内的吏民都具有法律的效力,任何人违犯了其中某一条“教令”是会受到惩罚的。《三国志》卷十二《司马芝传》,记芝在黄初中(220~226) 在河南尹任内“为教”与群下曰:
盖君能设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闻也。夫设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闻,吏之祸也。
汉代地方长官和他的属吏有“君臣之义”,故司马芝所说的“君”即是自称。我们由此更可见汉代郡守的权力之大,他们事实上可以是地方政府的“立法者”。但“设教”有一最重要的原则,即察人情、度时势;“教”之为“善”为“劣”由此而判。司马芝说“设教而犯,君之劣也”,即指一种违背人情和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教”。建安初何夔任长广太守,反对曹操为州郡所制的“新科”,曾指出:
所下新科,皆以明罚敕法,齐一大化也。所领六县,疆域初定,加以饥馑,若一切齐以科禁,恐或有不从教者。有不从教者不得不诛,则非劝民设教随时之意也。
“劝民设教随时”这六个字可以说是汉代“条教”的基本根据。
汉代郡守既有立法的大权,循吏自然便可以利用这种近乎绝对性的权力来规划他们的“条教”了。《后汉书·循吏列传·秦彭》:
建初元年(76年)迁山阳太守。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辄修升降揖让之仪。乃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吏有过咎,罢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怀爱,莫有欺犯。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塉,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郡县。于是奸吏跼蹐,无所容诈。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齐同其制。诏书以其所立条式,班令三府,并下州郡。
这个例子最便于说明循吏的“条教”问题。第一,秦彭所设之教是有“条式”的,这是“条教”的确解。第二,“条教”确是循吏自动自发地设立的,绝非奉朝廷之法令而行。不过由于秦彭对他所设计的一套“条教”特别自信,认为可加以普遍化,因此才建议朝廷,“宜令天下齐同其制”。这套“条教”虽“并下州郡”,但是否有强制性或曾否为其他州郡所采用,则不得而知了。
秦彭例子是发生在东汉章帝时代,章帝则是东汉最尊重儒术的皇帝,因此他对循吏的“条教”特别同情。但是循吏的“条教”和皇帝的意向并不是常常相合的。让我们再回头看看宣帝的态度。五凤三年(西元前55年) 黄霸为丞相,张敞上奏说:
“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有耕者让畔,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及举孝子、弟弟、贞妇者为一辈,先上殿,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不为条教者在后叩头谢。丞相虽口不言,而心欲其为之也。……臣敞非敢毁丞相也,诚恐群臣莫白,而长吏守丞畏丞相指,归舍法令,各为私教,务相增加,浇淳散朴,并行伪貌,有名亡实,倾摇解怠,甚者为妖。假令京师先行让畔、异路、道不拾遗,其实亡益廉贪贞淫之行,而以伪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诸侯先行之,伪声轶于京师,非细事也。汉家承敝通变,造起律令,所以劝善禁奸,条贯详备,不可复加。宜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郡事皆以义法令检式,毋得擅为条教;敢挟诈伪以奸名誉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恶。”天子嘉纳敞言,召上计吏,使侍中临饬如敞指意。霸甚惭。
张敞这篇奏议对于我们了解汉代“条教”问题有无比的重要性。首先必须指出:张敞此奏事实上完全合乎宣帝“汉家自有制度”的口味。他上此奏究竟是事先得到指示,还是因为他善于迎合上意,今已不得而知。但看“天子嘉纳敞言”和“霸甚惭”的叙述,则当时情事宛然如在目前。黄霸因为在郡守任内实行循吏的“条教”,得到皇帝特别的赏识而位至丞相,所以一旦身居相位便鼓励天下郡守都照他的“条教”办法治民。从奏文所引的内容,我们确知黄霸心目中的“条教”完全是儒家的“礼乐教化”。他在郡国上计时分长吏守丞为三等,而以“不为条教者”居殿,其意向确是很明显的。他的本意当然也是要讨好宣帝,但想不到反触其忌。我们不难想像,这次丞相、九卿等接见各地计吏的特殊安排在当时必引起了极大的政治风暴,“不为条教”的郡国计吏事后自不免怨声沸腾。“并行伪貌,有名亡实”之类的说法也许便是他们对“条教”所提出的控诉,而张敞即据之以上奏。这种控诉也未必毫无根据,但“条教”真正遭忌的地方则在“即诸侯先行之,伪声轶于京师,非细事也”。此“诸侯”可以指刘氏宗室诸王,也可以指一般郡守。前引严安上书已说明郡守之权太重,未尝不可能为乱。如果他们行“条教”的名声太大,对汉廷是可以构成政治威胁的。例如上面所引冯野王、冯立的“好为条教”,竟被当地吏民颂之为“鲁、卫之政”、比之为“周公、康叔”。在这种颂声中,吏民显然只知有太守而不知有皇帝了。
张敞奏文中之尤其重要的是将“汉家法令”和郡守“私教”之间的矛盾提升到对抗性的高度。这里也透露了汉代“政” 与“教”、“吏”与“师”之间的内在紧张。所以张敞最后提出“郡事皆以义法令检式,毋得擅为条教”。这便是后来朱博所说的“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郡守设“条教”则是以“师”自居,这似乎并不能博得宣帝的同情。所以张敞奏文时特别郑重叮咛郡守“举三老、孝弟等务得其人”。我们在前面已指出,三老、孝弟等是属于“乡官”的系统,即民间代表。从汉廷的立场说,三老才是真正“掌教化”的人。这个例子至少证明汉宣帝并不像表面上那样重视循吏的“教化”。我们在上文曾说汉廷对循吏抱着一种明褒暗贬的态度,其根据便在这里。又奏文中“毋得擅为条教”一语也不能看得太死,它的含义并不是禁绝一切“条教”,只是不要郡守设不符合“汉家法令”的“条教”而已。否则何以前引班固的《张敞传赞》竟说张敞本人“条教可观”呢?通过以上的分析,这篇奏文所显示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本文的若干主要论点如朝廷与儒教对“吏”的不同观点、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之分野,如真正有成效的“教化”多出于个别儒吏的文化使命感而非上承朝廷的旨意等,都可以从这篇奏文中获得不同程度的证实。
汉代循吏的“条教”都已失传,我们最多只知道其大概的内容,但不知究竟是怎样分“条”的。幸而《汉书·地理志下》保存了下面一条材料,可资参证。其文曰: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颜师古注:八条不具见):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
这条材料又可以与下面两条记载相参证。《三国志》卷三十《东夷传》“濊”条下则云:
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濊”条也说:
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置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已后风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余条。
箕子入朝鲜事是一个古代传说,无可考证。我们依史家时代先后罗列这一传说,旨在说明这个传说和“条教”的关系。《汉书》所记是代表最早的传说,《三国志》和《后汉书》则是根据《汉书》原文而重述。朝鲜史学家李丙焘讨论“箕子八条教”的问题,指出《汉书》并未言八条是箕子所“作”,陈寿和范晔都误读原文“织作”之“作”与下句相连。因此他认为所引“八条”中的三条是东夷民族旧原始法禁。 李氏说八条为东夷古法自是可能,但指责陈、范读破句则颇嫌牵强。《汉书》原文虽未明言箕子“作八条之教”,但读者若依上下文义而作此推断,也不能必证其出于误解。但我们特感兴趣的则在于三家所用的都是汉代“条教”的语言,而班固和范晔更是通过汉代循吏“先富后教”的观点去理解箕子的传说的。《汉书》所言“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则已不是传说而是汉代的事实了。这六十余条自是汉代郡守所设之“教”。所以由三书所记“箕子八条之教”,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汉代的“条教”大致是怎样一种形式。传说本身可信与否是另一问题,但传说终不能不通过某一特定的语言方式而存在。只要我们能确定其语言的时代背景,再无稽的传说也会留下明显的历史痕迹的。
我们已指出,“条教”在汉代并不是循吏的专利品。但是就两汉的记载而言,“条教”终是与循吏的关系较深。最低限度,少数受儒教熏陶的循吏曾企图运用守令的庞大权力把“条教”导入“先富后教”的方向,使“条教”之“教”名副其实。无论如何,后世的儒家大致是如此理解这个概念的。让我们引两条宋明新儒家的用法来结束关于“条教”的讨论。《河南程氏遗书》附录《门人朋友叙述》曰:
(明道)先生为政,条教精密,而主之以诚心。
明代宋仪望《赠邑侯任庵陈公入觐序》曰:
吾吉守湘潭周公以廉明仁爱为诸令先。诸所条教,动以儒雅饰吏治。
这两处“条教”的含义自然是和循吏的观念分不开的。
(八)结语
以上我们大致讨论了汉代循吏在传播文化方面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我们必须紧接着指出,汉代循吏的人数毕竟是很少的,远不及酷吏和俗吏那样人多势众。所以我们决不能说,中国文化的传播主要是少数循吏的贡献。事实上,循吏不过是汉代士阶层中的一个极小的部分而已。但是由于他们能利用“吏”的职权来推行“师”的“教化”,所以其影响所及较不在其位的儒生为大。汉代处士而德化一乡者也不乏其人,如皇甫谧《高士传》中人物,如《后汉书》中隐逸独行之士,如《党锢传》中人物(蔡衍即是一例) 。汉末避难的士人也把中原文化传播到边区如交州,河西、辽东都因此而保存了中原的大传统。《三国志》卷十一《管宁传》引《傅子》云:
宁往见(公孙)度,语惟经典,不及世事。还乃因山为庐,凿坏为室。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由是度安其贤,民化其德。
这不过是偶举一例而已。循吏是士的一环,其影响主要是在文化方面,这种潜移默化的效用也不是短期内所能看得见的。循吏在表面上是“吏” ,在实质上则是大传统的传播人。这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产品。所以西方学者稍一接触这一型的人物,便可以立刻看出他们身负着“文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 。汉王朝灭亡之后,中国统一的观念并未随之而去,因此下面仍有隋、唐的继起。但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便再也没有看到第二度的统一了,所谓“神圣罗马帝国”不过一个空壳子而已。如果说欧洲中古以后仍统一于“基督天下”(Christendom) ,那也是“教”的功用。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有一点极明显的不同,即罗马的“郡守”(provincial governor) 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循吏”。罗马史的专家毫不迟疑地指出:我们必须牢记一件事实,即罗马人从未意识到他们是较高文化的传教人,因而觉得有神圣的义务将自己的文化加诸属民。他们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们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语言、宗教以至政治组织方面的事。他们在这些事上是不肯加以干涉的。这种宽容当然也有一个限度,即和平得以维持,属民照常纳税并满足政府对于服兵役的合理要求。 但是必须声明:我们在这里只是指出异同,而不是判断优劣。
《朱子语类》卷一三五曰:
汉儒初不要穷究义理,但是会读、记得多,便是学。
朱子的观察是相当深刻的,汉儒在哲学理论上确是“卑之无甚高论”。他们只读了少数几部经典,深信其中的道理,然后便尽量在日常人生中身体力行。循吏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们相信“教”比“政”更重要,因此不但以“师”自许、自荣,更崇敬社会上人人景仰的经师、人师。孔融为北海相,“崇学校,设庠序,举贤才,显儒士” 。这是典型的循吏风范,不但如此,他“告高密县为郑玄特立一乡,名为郑公乡”。同书又引司马彪《九州春秋》曰:“融在北海……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会而已。……高密郑玄,称之郑公,执子孙礼。”重“师”远过于重“吏”,即孔融之例可见。孔融不需高谈道统高于政统的理论,他的行动已说明他的价值取向何在。这种风气并不限于循吏,而遍及朝廷公卿。欧阳修《集古录》卷二“孔庙碑阴”条下云:
汉世公卿教授,聚徒常数百人,亲受业者为弟子,转次相传授为门生。
我们当然也可以对这种现象提出一种社会学的解释,譬如说这是因为门生弟子构成公卿的社会、政治基础。但是这种解释虽有理有据,却仍不足以取消另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它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师”重于“吏”、“教”高于“政”。换句话说,儒家的价值观念也不知不觉地随着这种风气的激荡而渗透到社会意识的深处。循吏本身所产生的直接社会影响也许是微弱的,他们所树立的价值标准则逐渐变成判断“良吏”或“恶吏”的根据。我们已经看到汉碑上对“循吏之道”的公开颂扬。现在让我们再从反面看看酷吏的社会形象。《汉书·酷吏严延年传》:
后左冯翊缺,上欲征延年,符已发,为其名酷,复止。
宣帝的内心是欣赏严延年的,但是他终不能不向大传统公认的价值标准低头。“酷吏”究竟是见不得人的。
汉代循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长远影响还是不容低估的。宋、明的新儒家在义理的造诣方面自然远越汉儒。但是一旦为治民之官,他们仍不得不奉汉代的循吏为最高准则。别的不说,他们以“师”而不以“吏”自居便显然是直接继承了汉代循吏的传统。程、朱、陆、王无不是一身而兼两种“师”:大传统的“传道、授业”之师和小传统的“教化”之师。朱子重建白鹿洞书院便是师法循吏的成规,不是出于“吏职”的要求。陆象山在荆门讲《洪范》则是用大传统来改造小传统。这一类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若以治民而言,吕坤《实政录》卷二《民务、养民之道》云:
养道、民生先务,有司首政也。故孔子答子贡之问政曰:足食。答冉有之在卫曰:富之。王道有次第,舍养而求治,治胡以成?求教,教胡以行?无恒产有恒心,士且不敢人人望,况小民乎?成周养道,不可及矣。
这岂不正是汉代循吏言论的翻版吗?洪榜《戴先生行状》曰:
先生抱经世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为常称《汉书》云: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祠,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先生未尝不三复斯言也。
戴震生平与宋儒争义理是非,呶呶不休,然而他的一瓣心香却永远在汉代的循吏。这是大足发人深省的。
原始儒教不尚“空言”,但求“见之行事”。孔子所讲的都是一些当时人人可以懂得的人生大道理。儒教当然也有它的系统,但是至少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其中自然的脉络似乎多于人为的建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所以儒教不求“最后之因”、不问“第一原理”。孔子也许对“性与天道”都有自己的深刻了解,但那也是“但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孔子所始终关心的则在天下是有道还是无道。他把变无道为有道的责任首先加于“士”的身上,这便是所谓“士志于道”。总之,原始儒教要求“士”根据人人共见共喻的大道理,努力将我们的世界改得更好一点。天下愈是无道、愈是昏暗,“士”的改造世界的责任也愈大。马克思说:“哲学家从来都在以各种方式来解释世界,但真正的关键是改变它。”这个名言也许适用于西方史上的哲学家,但对于中国史上的“士”而言,则适得其反。如果我们从西方的观点来批评中国思想,特别是儒家,我们可以说儒家的最大缺点正在于对世界的解释工作做得不够,特别是逻辑系统严整的解释。但是对于人的世界而言,解释是永远落后着的。等到哲学家把世界解释清楚了,这世界早已变了。黑格尔认为只有在真实世界已衰落的时候,哲学才会开始,大概便是指着这种“落后着”的情况而言的。中国的“士”则不能坐视世界的衰落而无动于衷,他们无论在平时或在乱世,都不能忘情于怎样变无道为有道。汉代儒教的最大功效便是在于塑造了第一批这样的“士”。循吏则代表了其中比较独特的一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七“两汉风俗”条说: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常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粃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故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闚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可谓知言者矣!
亭林对汉代儒教兴起的解释未必恰当。且其言复别有所感,这里都毋须深究。不过他对于东汉“士”的精神则把握得非常深刻。他引用《诗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以象征儒教熏陶下的中国的“士”,尤为传神。这使我们联想到黑格尔在《权利哲学》序中对西方哲学所作的象征性的刻画。他的话如果仿照《诗经》体翻译成中文,大概可以说是“暮色既晦,夜鹰展翼”(The owl of Minerva spreads its wings only with falling of the dusk. ) 。这两个象征的对比生动地显示出中西文化的不同风格。中国的“士”和西方的“哲学家”毕竟各自形成了独特的传统。为什么循吏出现在汉帝国而不见于罗马帝国?这至少是一个耐人深思的问题。
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
(一)引言
东汉初期帝王如光武、明帝、章帝等都比较尊重士人,这是大家所习知的。而且光武本人也是士人出身,曾于“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后汉书·光武帝纪》) 。所以虽在东西诛战之际,犹能“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樊准语) 。赵翼《廿二史札记》论“东汉功臣多近儒”条云:
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
赵氏看出了两汉开国君臣的性质不同,确是他的史识过人之处。然而他把这一重要事实单纯地解释为“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与“性情嗜好之相近”,而不能从历史的与社会的背景上看问题,却未免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我们根据赵氏这一段文字所启示的线索,而将两汉政权建立时社会背景的主要差异,加以比较研究,便可对东汉政权的本质,及西汉末叶至东汉初期这一阶段的政治史,有比较深入的认识与贯通性的解释。并因而了解到,在赵氏所指出的两汉开国君臣性质不同的背后,还埋藏着一些可以说明两汉社会变迁的重要事实。
(二)士人数量的激增
从历史记载上我们可以看出,私人教授的风气愈往后愈普遍。所以班固的《儒林传》赞曰: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三)士族的形成探源
可是我们不能把这种人数的增多单纯地理解为力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士人的社会身份已随着这种增加而发生了本质的改变。西汉政权之建立,士人虽未发挥重要的作用,但高祖阵营中还是有少数儒生如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这些人的社会本质如何呢?稍一回想便可知道:他们还是和战国时单身的“游士”没有什么分别;他们除了知识之外,别无其他的社会凭借。叔孙通虽带了一百多个学生,在天下未定之前,却一直被冷落在一边。但在西汉末叶,士人已不再是无根的“游士”,而是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士大夫”了。这种社会基础,具体地说,便是宗族。换言之,士人的背后已附随了整个的宗族。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
然则,士与宗族又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呢?这一问题,若详加分析,必须另有专文。我们在此只能略加探溯,以明源流所自而已。家族群居之制源自远古,本非汉代的新产物。秦与汉初的移徙大族政策,一部分用意便在于防止封建宗族势力的复活 。武帝时更有强宗大姓不得族居的禁律。《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书说:
其(郑弘)曾祖父本齐国临淄人,官至蜀郡属国都尉。武帝时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将三子移居山阴,因遂家焉!(又《北堂书钞》四○、七八引)
可见传统的宗族势力一直很强大,而为西汉统治阶层所畏惧。然而这种宗族势力与士人之间并未发生具有社会含义的联系,故其性质应与后来的“士族”有别,未可混为一谈。我们试举一例以说明之。《史记·主父偃列传》记偃之言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后偃拜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又见《汉书》本传)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在武帝之世,士与宗族还没有完全打成一片。从此一故事与苏秦的传说之相似性来看,可见那时的士人仍未脱离“游士”阶段。此外如流传颇广的朱买臣的故事,也具有同样的社会意义。其所以如此者,最根本的原因,显然是由于那时的士尚未能普遍地、确定地取得政治地位,因此也就不能形成他们的宗族。但在武帝崇儒政策推行之后,士人的宗族便逐渐发展。如《史记·酷吏列传》记张汤“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及汤死,“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汉书·张汤传》同) 。自此以后,士与宗族的关系便日深一日。杨恽“受父财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后母无子,财亦数百万,死皆予恽,恽尽复分后母昆弟。再受訾千余万,皆以分施”(《汉书》本传) 。朱邑“身为列卿,居处俭节,禄赐以共九族乡党,家亡余财”(同书《循吏传》,又见《前汉纪》卷十九) 。疏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卖以共具”(同书本传,又略见《前汉纪》卷十八) 。严延年母知子将败,“遂去。归郡,见昆弟宗人,复为言之”(同书《酷吏传》,又《前汉纪》卷十九作“母还归,复为宗族昆弟言之”) 。平当不应封侯之诏,“宗族皆谓当曰:何不强起受侯印绶为子孙邪?当曰:吾在大位已负素餐之责矣!起受侯印,还寝而死,死有余罪。今不起者为子孙也”(《前汉纪》卷二十八,又《汉书》本传,“宗族”作“家室”) 。《汉书·鲍宣传》:“(郇) 越散其先人訾千余万,以分施九族州里。”张临“亦谦俭。且死,分施宗族故旧”(同书《张汤传》) 。
我们将这几条史实与主父偃的宗族关系作一对照,便立刻可以看出士与宗族的关系,在武帝以后发生了如何巨大的变化。至于这种变化的实际过程究竟如何,由于文献不足,我们无法详说,唯亦有蛛丝马迹可得而言者。士族的发展似乎可以从两方面来推测: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再转而扩张家族的财势。这两方面在多数情形下当是互为因果的社会循环。所谓“士族化”便是一般原有的强宗大族使子弟读书,因而转变为“士族”,这从西汉公私学校之发达的情形,以及当时邹鲁所流行的“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 的谚语,可以推想得之。试想读书既为利禄之阶,岂有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强宗大姓反而不令子弟受学之理?而且这种推想也并不是全无事实根据,例如平当“祖父以訾百万,自下邑徙平陵。当少为大行治礼丞,功次补大鸿胪文学,察廉为顺阳长,栒邑令,以明经为博士”(《汉书》本传) 。历史上只说他家世豪富,并未说他是仕宦世家,很可能是到平当这一代才开始读书的。比较明显的例子是萧望之。《汉书》本传说他“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这是普通强宗大姓转变为士族的确证。后世谱牒妄记望之为萧何之后,颜师古已力辨其非。又如郑崇“本高密大族……祖父以訾徙平陵。父宾明法令,为御史”(同书本传) 。可见郑氏也是刚由普通大姓转变为士族的。西汉自武帝以后,必然有许多强宗大姓逐渐转变为士族,此实属不容怀疑的事。我们只要进而一察士人借政治关系发展宗族财势的情形,对这一点便可有更明确的认识。《汉书·张禹传》说:“(禹) 河内轵人也,至禹父徙家莲勺(师古曰:左冯翊县名。) ……(卜者) 谓禹父:‘是儿多知,可令学经。’”同传又说“家以田为业”。可见张禹原为大姓子弟。西汉多强宗大姓迁徙之事,张家当亦为其中之一(如前举郑崇之例) 。及至张禹在政治上得势之后,便极力为宗族求发展:“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禹每病,辄以起居闻,车驾自临问之。上亲拜禹床下,禹顿首谢恩,因归诚,言‘老臣有四男一女,爱女甚于男,远嫁为张掖太守萧咸妻,不胜父子私情,思与相近’。上即时徙咸为弘农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临候禹,禹数视其小子,上即禹床下拜为黄门郎,给事中。”其后禹卒,“(长子) 官至太常,列于九卿。三弟皆为校尉散骑诸曹”。(均见《汉书》本传,又略见《前汉纪》卷二十五) 又如杨恽“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岁余,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孙会宗……与恽书谏戒之,为言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同书本传) 。郑崇以谏哀帝勿过宠外戚近臣获罪,尚书令奏崇与宗族通,疑有奸,请治。“上责崇曰:‘君门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对曰:‘臣门如市,臣心如水。’”(同书本传) 是崇亦承认他与宗族的关系甚为密切。疏广归乡里,“居岁余,广子孙窃谓其昆弟老人广所爱信者曰:‘子孙几及君时颇立产业基址,今日饮食费且尽。宜从丈人所,劝说君买田宅。’老人即以闲暇时为广言此计,广曰:‘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说服”。(同书本传) 疏广为士人中之贤者,所以不肯过分为家族治“产业基址”,但他的家族经济状况还是很好,而且从他所谓“吾岂老悖”之言观之,则士人为家族治产的思想,在当时已甚为普遍。可是士人中究竟贤者太少,故利用政治关系发展家族势力者,比比皆是。武帝时,丞相公孙贺便是其中之一。征和二年春诏曰:“故丞相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朕忍之久矣!终不自革……”(《汉书·刘屈氂传》) 士族势力的发展,最后竟至侵犯到一般平民的利益,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汉时有识之士便已看到这一点,元帝时贡禹陈事已指出当时风气,以“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杰,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同书本传) 。哀帝时鲍宣上书也说“豪强大姓蚕食亡厌”,为民“七亡”之一;他指出:“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又说:“臣虽愚戆,独不知多受禄赐,美食太官,广田宅,厚妻子,不与恶人结仇怨,以安身邪?”(均见本传) 这些话实透露出当时大族发展的黑暗的一面。
上引史实已可说明西汉士族势力的产生过程及其活动方式,用不着再加解释。我们固不能说那时所有强宗大族都已“士族化”,但士族在西汉后期的社会上已逐渐取得了主导的地位,实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我们懂得了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就可以进一步讨论从西汉末叶至东汉政权建立这一期间的政治变迁了。
(四)王莽兴亡与士族大姓的关系
士族势力的政治影响,首先具体表现在王莽的变法运动上。王莽本人是当时两种矛盾的社会势力的综合产物:从他的身世来说,他乃是外戚,属于王室势力的系统;但从其行事及其所推行的政策看,则他又代表了汉代士人的共同政治理想。他之所以后来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便正是由于他一方面有王室的关系为凭借,而另一方面又获得了不少士人的归心。前面曾指出士与家族的关系愈至后便愈密切,外戚的宗族势力似乎也有同样的发展过程。例如武帝方幸王夫人时,宁乘对卫青说:“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贵。愿将军奉所赐千金为王夫人亲寿。(师古曰:亲,母也。)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则那时的外戚与家族之关系还不一定都很密切。但无论如何,到昭帝时,外戚与家族的关系便已经很深了。霍光死后,魏相奏封事说:“今光死,子复为大将军,兄子秉枢机,昆弟诸婿据权势,在兵官。光夫人显及诸女皆通籍长信宫……”(《汉书·魏相传》) 《后汉书·申屠刚传》载,刚对策论外戚事有云:“霍光秉政,辅翼少主,修善进士,名为忠直,而尊崇其宗党,摧抑外戚。”章怀注曰:“昭帝时霍光辅政,其子禹及兄孙云、山等皆中郎将、奉车都尉,昆弟诸婿皆奉朝请,给事中,唯昭帝外家赵氏无一在位者。”其论外戚与宗族之关系亦自霍氏始,不更上溯。可见武帝以后外戚与宗族之关系确有一转变。而且外戚之富贵者,也不止于本族了。成帝时,张匡便以此攻击王商。他说商“宗族为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诸曹给事,禁门内连昏诸侯王,权宠至盛。”又说:“今商宗族权势,合资巨万计,私奴以千数。”(同书《王商传》) 后商死,其“子弟亲属为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补吏”(同上) 。可见张匡所言并不为过分。《前汉纪》载成帝元延元年刘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而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称举者登进,忤恨者中伤,游谈者为己说,执政者为己言。……兄弟据重,家族盘牙。历自上古以来,未有其比。”(卷二十七) 我们举此数事以见西汉的外戚,亦自有其家族的背景。王莽既有大志,当然也不能忽略这一力量。所以他年轻时:“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阳朔中,世父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这种孝弟之行,显然是为了取得宗族的信任。及后为安汉公时,又“复以千万分予九族贫者”(均见《汉书》本传) 。则交结宗族之意尤为明显,且范围也远超出本族之外了。而王莽之得势,更重要的还在于他获得了多数士人的支持,这是一般外戚不能和他比较的地方。他早年即以士人而不是外戚姿态出现:“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汉书》本传复记他后来和士人交往的情形云:
……(莽)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恧。
莽兄永为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学博士门下。莽休沐出,振车骑,奉羊酒,劳遗其师,恩施下竟同学。诸生纵观,长老叹息。
因此一时名士如戴崇、金涉、箕闳、阳并、陈阳等都成为他的支持者。及后执政,遂有宗族与士人结党为莽效力之事:
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本传)
“外交英俊,内事诸父”的策略,终使王莽同时赢得了士人与宗族的拥戴,故班固也不能不承认:“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士友归仁。”(《王莽传》赞)
王莽兴起之士人与宗族的背景既如上述,而新室的失败,也与其时的士族大姓有相当关系,值得我们注意。在未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必须辨明:即个别士人的社会理想并不必然和他自己阶层的利益完全符合。换言之,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常表现为追求社会的正义与进步。这也是一般社会所以尊重士人的主要原因。即以两汉而论,自董仲舒以迄仲长统,许多明智之士,都感觉到豪强兼并是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故多主张限田或井田之类的均田政策,以消弭贫富过分悬殊的现象。而在两汉豪强大姓之中,则颇不乏士族之家,观前所举士族兴起之事实可知。贡禹、鲍宣的议论,更显然是以士族为对象。此外两汉许多打击豪族大姓的所谓酷吏,也多可以归之于这一类士人之中。而且无论我们对这一类现象如何解释,个别士人的言行可以超越他所属的阶层利益,终为不可抹杀的客观事实。王莽新政的失败,便恰恰是说明这项原则的例证之一。
在王莽新政所表现的社会理想中,限制士族大姓在经济上的过度扩张,是最主要的项目之一。这种限制后来便具体化为复井田与禁奴婢。盖土地兼并与奴婢买卖为当时士族大姓势力发展之一要端。哀帝时,师丹建言说得很明白:
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汉书·食货志上》)
荀悦更对豪强兼并下的实际情形有深入的分析,他说:
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而豪富人占田逾侈,输其税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前汉纪》卷八)
王莽新政便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危机下产生的。这种政策的推行,很显然地要侵害到士族大姓的利益,因之,其将引起士族大姓的普遍反对,也可以说是必然的。我们且先看一看王莽失败的前奏曲。
原来在师丹建言之后,哀帝即令“下其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食货志上》) 。这种政策,姑无论其是否足够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倘真能付诸实施,总可发生一点压抑豪强大姓的作用。 可是结果如何呢?《食货志》接着告诉我们:
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师古曰:丁、傅及董贤之家皆不便此事也)诏书且须后。(师古曰:须,待也)遂寝不行。
这样一种轻微的改革都因为不便于权贵之家而胎死腹中 ,何况是王莽那种比较激烈的政策呢?荀悦论井田制度的实行云:
夫井田之制,宜于民众之时,地广民稀,勿可为也。然欲废之于寡,立之于众,土地既富,列在豪强,卒而规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前汉纪》卷八)
荀氏之言本为泛论,但竟道中了王莽失败,天下乱起的一部分原因。我们观察旧史的记载,至少可以看出一点,即当时真正为反对王莽新政而起兵者,主要是一些士族大姓 。更堪玩味的是,在其复井田禁奴婢未正式实行以前,士族大姓犹有拥戴新室者,而起事者亦甚少,在这以后,天下士族大姓遂纷纷起兵反叛。我们于此须先对士族大姓的社会势力及其举兵的历史略加追溯。
汉初豪宗强族多为古代封建势力之遗,故汉廷对付他们的政策,除迁徙之外,便是严厉的打击,甚至不惜加以“夷灭”。此观《史记·酷吏列传》可知。武帝以后,强宗豪族既逐渐因“士族化”而与统治阶层发生联系,其势力遂益为巩固与浩大。而一般对付豪强的官吏,便往往要采取分化与利用的政策,不能一味地杀伐了。宣帝时,赵广汉迁颍川太守:
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广汉既至数月,诛原、褚首恶,郡中震栗。
先是,颍川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广汉患之,厉使其中可用者受记,出有案问,既得罪名,行法罚之,广汉故漏泄其语,令相怨咎。又教吏为缿筒,及得投书,削其主名,而托以为豪杰大姓子弟所言。其后强宗大姓家家结为仇雠,奸党散落,风俗大改。吏民相告讦,广汉得以为耳目,盗贼以故不发,发又辄得。一切治理,威名流闻。(《汉书·赵广汉传》)
这显然只是治标的办法,并不能真正消弭社会危机,而且还引起了另一方面的恶果。因此后来韩延寿继治颍川遂改弦更张,运用软化的手段。同书《韩延寿传》说:
颍川多豪强,难治……先是,赵广汉为太守,患其俗多朋党,故构会吏民,令相告讦,一切以为聪明,颍川由是以为俗,民多怨仇。延寿欲改更之,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
这便是西汉循吏所常推行的教化政治。观其以“长老”为号召的办法,则主要还是借重宗族的关系,不过纳之于礼义之途而已!至于其效果是否如历史上所说的那样神速,我们已无从知悉,也无须乎深究。我们于此应注意的是,这种教化政治,仍是两汉士人所向慕的士族社会的共同理想。因之,如果这种政治实验真是相当成功,则更足以说明当时社会士族化的程度实已很深了。此外如成、哀之世的朱博,也是以分化政策治理豪族大姓著称,史载:
博治郡,常令属县各用其豪杰以为大吏,文武从宜。县有剧贼及它非常,博辄移书以诡责之。其尽力有效,必加厚赏,怀诈不称,诛罚辄行。以是豪强慹服。(《汉书·朱博传》)
很显然的,这一类的政策所能发生的作用,最多也不过是防止强宗大姓为非作歹而已,它不但不能遏止豪强势力的正常发展,从另一方面说,恐正有以助长之。偶有严厉打击豪强者,则已不能立足,如陈咸在州郡:“下吏畏之,豪强慹服,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见废。”(同书《陈万年传》)
西汉强宗大姓的势力如此庞大,故中叶以降,已常有造反之事,如“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齐孝王孙泽交结郡国豪杰谋反,欲先杀青州刺史”(同书《隽不疑传》) 。这已是大姓举兵的明证。成帝河平三年:“广汉男子郑躬等六十余人攻官寺,篡囚徒,盗库兵,自称山君。”次年冬,“广汉郑躬等党与寖广,犯历四县,众且万人”。(《成帝纪》) 梅福上疏论士之重要曾引此事为例云:“方今布衣乃窥国家之隙,见间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注:“成帝鸿嘉中,广汉男子郑躬等反是也。”(见《梅福传》) 参而考之,则郑躬似为士人。无论如何,士族在西汉末叶已颇有势力,殆为显著的事实。梅福曰:“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同上) 李寻谓王根曰:“夫士者国家之大宝,功名之本也。”(同书《李寻传》) 后光武亦谓王霸曰:“今天下散乱,兵革并兴。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梦想贤士共成功业,岂有二哉!”(《后汉纪》卷一) 此等思想只有在士族势力既兴之后才能滋长,绝非汉初社会所能普遍流行的。而且这些话也并不是虚语,当时确有因得士而兴或失士而败者。宣帝时杨恽之死便因为他“自伐其贤能,性好刻害,发人阴伏,轻慢士人,卒以此败”(《前汉纪》卷二十) 。又如朱邑也“贡荐贤士大夫,多得其助者”(《汉书·朱邑传》) 。哀帝时,朱博“好乐士大夫。为郡守九卿,宾客满门,欲仕宦者荐举之,欲报仇怨者解剑以带之。其趋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终用败”(同书《朱博传》) 。
我们明白了王莽变法以前士族大姓的实际力量,对于王莽时士族大姓纷纷起兵的现象,就不会感到突兀了。前面说过,王莽虽一方面交结士大夫,另一方面却又打击侵凌小民的豪强势力,这是与多数士族大姓的利益相冲突的。史载:“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阴有篡国之心,乃风州郡以罪法案诛诸豪杰及汉忠直臣不附己者。”(《汉书·鲍宣传》,又见《王莽传上》) 这已经开始惩治豪强了,其始建国元年改制诏有云:
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按此或即前引荀悦之论之所本)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汉书·王莽传中》)
这种改革之不利于一般士族大姓,可不待言而明。因此其后“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同上) 。而当时起事反莽之士族大姓亦多以此。卜者王况谓李焉曰:“新室即位以来,民田奴婢不得卖买……百姓怨恨,盗贼并起。”(同书《王莽传下》) 隗嚣移檄数莽罪状,亦列“田为王田,卖买不得”为其中之一(《后汉书·隗嚣传》) 。甚至王莽自己的人也有同样的看法。区博谏王莽曰:
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王莽传中》)
区博的话已明确地指出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王莽为巩固政权计,亦不能不作某种程度的让步,故下书曰:“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同上) 其后叛乱四起,莽召问群臣擒贼方略,公孙禄也说:
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牺和鲁匡设六管,以穷工商。说符侯崔发阿谀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王莽传下》)
综合以上种种材料观之,可见复井田与奴婢之禁,确是激起士族大姓反莽的基本原因之一。
因此,地皇三年,“莽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管之禁”。我们试一看最早起兵反莽者的社会身份,对此点便可有更深切的认识。居摄元年四月,“安众侯刘崇与相张绍谋曰:‘安汉公莽专制朝政,必危刘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举,此宗室耻也。吾帅宗族为先,海内必和。’绍等从者百余人”。此刘氏之宗族也。次年东郡太守翟义见王莽居摄,心恶之,谓姊子上蔡陈丰曰:“‘吾幸得备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汉厚恩,义当为国讨贼……今欲发之,乃肯从我乎?’丰年十八,勇壮,许诺。又遂与东郡都尉刘宇、严乡侯刘信、信弟武平侯刘璜结谋。……郡国皆震。比至山阳,众十余万。莽闻之,大惧。”(《汉书·翟方进传》) 此士族与宗室之连结者也。翟义兵既起,“槐里男子赵明、霍鸿等起兵,以和翟义,相与谋曰:‘诸将精兵悉东,京师空,可攻长安。’众稍多,至且十万人”(《王莽传上》) 。此则普通大姓也。
唯以上几次士族大姓的反叛,都在王莽篡位之前,那时王莽的改制尚未明朗化,所以士族大姓和者犹少。而且由于王莽一向颇得士人的拥戴,在其复井田禁奴婢未施行之前,尚有士族大姓助莽平乱者。此事甚有意义,兹举数例以明之。刘崇、张绍起兵时,崇族父嘉与绍从弟竦“诣阙自归,莽赦弗罪”。竦复为嘉作奏曰:“安众侯崇乃独怀悖惑之心,操畔逆之虑,兴兵动众,欲危宗庙,恶不忍闻,罪不容诛。……是故亲属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溃畔而弃其兵。”又说:“方今天下闻崇之反也,咸欲骞衣手剑而叱之……而宗室尤甚。……宗室所居或远,嘉幸得先闻,不胜愤愤之愿,愿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负笼荷锸,驰之南阳。”(均见《王莽传上》) 刘敞子祉娶翟宣女为妻,“会宣弟义起兵欲攻莽,南阳捕杀宣女,祉坐系狱。敞因上书谢罪,愿率子弟宗族为士卒先”(《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 。甚至在王莽篡位之后,宗室及一般士族大姓仍有助莽之事。“始建国元年四月,徐乡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于其国。快兄殷,故汉胶东王,时改为扶崇公。快举兵攻即墨,殷闭城门,自系狱。吏民距快,快败走,至长广死。莽曰:‘……今即墨士大夫复同心殄灭反虏,予甚嘉其忠者,怜其无辜。其赦殷等,非快之妻子它亲属当坐者皆勿治。”(《王莽传中》) 这是王莽改制前的最后一次叛乱。自此以后,遂不见有士族大姓拥戴新室之记载。相反的,各地士族大姓都纷纷率领宗族子弟起而反莽,王莽政权终因而覆亡。王莽亦深知他的政策不利于一般士族大姓的社会经济利益,所以天下乱起之后,他最忧虑的也是士族大姓的武装力量。地皇二年,莽下书责吏士而论及盗贼的性质云:
今……盗发不辄得,至成群党,遮略乘传宰士。士得脱者,又妄自言:“我责数贼‘何故为是?’贼曰‘以贫穷故耳’。贼护出我。”今俗人议者率多若此。唯贫困饥寒,犯法为非,大者群盗,小者偷穴,不过二科。今乃结谋连党以千百数,是逆乱之大者,岂饥寒之谓邪?(《王莽传下》)
王莽不信饥寒为盗之说,当然是由于他了解士族大姓造反的可能性较大之故。我们看了下面这一记载当更了然:
初,京师闻青、徐贼众数十万人,讫无文号旌旗表识,咸怪异之。……莽亦心怪,以问群臣,群臣莫对。唯严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黄帝、汤、武行师,必待部曲旌旗号令,今此无有者,直饥寒群盗,犬羊相聚,不知为之耳。”莽大说,群臣尽服。及后汉兵刘伯升起,皆称将军,攻城略地,既杀甄阜,移书称说。莽闻之忧惧。(《王莽传下》)
按此所谓“青、徐贼众”,即赤眉也。王莽不畏“饥寒群盗”而独惧刘伯升者,盖以前者仅为下层农民的乌合之众,不足成事,而后者则为士族大姓的集团,具有深厚的社会势力故耳!因此地皇四年王莽大赦天下时犹曰:“故汉氏舂陵侯群子刘伯升与其族人婚姻党与,妄流言惑众,悖畔天命……不用此书。”可见王莽对于饥民集团与士族大姓势力之区别,固辨之甚明也。观翟义起兵时“王莽日抱孺子会群臣”及“作大诰”种种张皇失措的表现,则更可推想他对士族大姓势力的戒惧为何如矣!
(五)两汉之际起兵群雄的社会背景
从王莽政权的崩溃至东汉政权的建立这一期间,士族大姓的势力表现得更为显著。我们对这一期间的剧烈政治变迁加以分析,便可看出东汉政权与士族大姓之间的关系如何密切,而王莽失败的根本原因亦可因之而益明。
(六)两汉之际士族大姓的举宗从征
前面我们简要地清理了东汉政权建立之前,各地士族大姓的起兵以及几个主要武装集团各据一方的混乱历史。我们于此至少已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时起事者实多属强宗大姓,而称霸的群雄更非有强宗大姓的支持不可。唯关于士族的问题,许多更重要的史实,上文犹未及征引。我们将于下面分析东汉政权的性质时,进一步讨论之。如此则上文一些没有交代清楚的关键可迎刃而解。我们在前面已一再提到士族大姓的问题,可是由于旧史家对当时扰乱的群雄之身世背景等叙述得过于简略,除少数情形外,我们已很难找到关于士族大姓实际活动的明确记载。因此到现在止,读者对士族大姓起兵的普遍性,恐仍不能无疑。幸而光武集团以及许多附汉的士族大姓的动态,旧籍中均保存了许多史料,若细加排比,则事实昭然若揭。
(七)宗族的武装自保及其方式
以上所举仅为随光武征战之士族势力,至于以其他方式支持光武集团之士族,则均未列入。如“宋弘字仲子,京兆长安人也。父尚,成帝时至少府……弘少而温顺,哀平间作侍中,王莽时为共工……光武即位,征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为大司空,封栒邑侯。所得租奉分赡九族”(《后汉书》本传) 。宣秉“少修高节,显名三辅”。后仕光武,“所得禄奉,辄以收养亲族。其孤弱者,分与田地”(同书本传) 。杜林,“父邺,成哀间为凉州刺史。林少好学沈深,家既多书,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等皆是。今不详引。此外尚有许多宗族自保的集团,亦为当时社会上一极普遍的现象。其最大者如窦融、梁统等在河西五郡,事已见前。又有保全一郡者,如伏湛在平原,侯霸在淮平(均见同书本传) ,苏竟在代郡,鲍永、田邑等在并土(同书《冯衍传》、《鲍永传》) ,都能在兵革之中捍卫宗族,庇护黎庶。史文甚长,不能多所征引。我们这里且一看分散各地的宗族自保集团。所谓自保,即虽拥兵众而无意于争夺政权者。《后汉纪》卷一贾复说刘嘉曰:“今汉氏中兴,大王以亲戚为辅。天下未定而安所保,所保得无不可保乎?”嘉曰:“公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马刘公在河北,可往投之。”《后汉书·伏湛传》:“时门下督素有气力,谋欲为湛起兵,湛恶其惑众,即收斩之。”又同书《虞延传》:“王莽末,天下大乱,延常婴甲胄,拥卫亲族,扞御钞盗,赖其全者甚众。”此数事均证明当时武装宗族集团中,确有仅以自保为最高目的者。同书《刘盆子传》:“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遗人往往聚为营保,各坚守不下。”又赤眉夺长安时“百姓保壁,由是皆复固守”(同上) 。《冯异传》:“时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众。”《陈俊传》:“五校引退入渔阳,所过虏掠。俊言于光武曰:‘宜令轻骑出贼前,使百姓各自坚壁,以绝其食,可不战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将轻骑驰出贼前。视人保壁坚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贼至无所得,遂散败。” 这是士族大姓在兵革中自卫的一般情形。我们再看几个具体的例子:
1.樊宏:“更始立,欲以宏为将,宏叩头辞曰:‘书生不习兵事。’竟得免归,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后汉书》本传)
2.冯鲂:“为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溃畔,鲂乃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以待所归。”(同书本传)
3.第五伦:“王莽末,盗贼起,宗族闾里争往附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铜马、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皆不能下。”(同书本传)
4.简阳大姓:“时江南未宾,道路不通,以憙守简阳侯相。憙不肯受兵,单车驰之简阳。吏民不欲内憙,憙乃告譬,呼城中大人 ,示以国家威信,其帅即开门面缚自归,由是诸营壁悉降。”(同书《赵憙传》)
5.赵纲:“光武即位,拜(李章) 阳平令。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同书《酷吏列传》)
按营壁、壁垒、营保或营堑原为军事建筑物。《史记·项羽本纪》:“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又《淮阴侯列传》:“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即是也。故《西汉会要》卷五十七列“壁垒”于“兵”项下。两汉之际,战役中用之尤多,史不胜书。如《耿弇传》:“与中郎将来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诸营保,皆下之。”同传载张步言:“以尤来、大彤十余万众,吾皆即其营而破之。”又注引《袁山松书》曰:“弇上书曰:‘臣据临淄,深堑高垒,张步从剧县来攻,……臣依营而战……’”《杜茂传》:“击五校贼于魏郡、清河、东郡,悉平诸营保。”《马成传》:“令诸军各深沟高垒。宪数挑战,成坚壁不出。”《张宗传》:“诸营既引兵,宗方勒厉军士,坚垒壁,以死当之。”此种记载俯拾即是,略举数例以见当时营壁之普遍。从一般士族大姓筑营壁以自保的事实,我们更可看出他们势力的浩大。这种民间的营壁,并非乌合之众,其中亦有组织,故有所谓“营长”,盖即宗族集团之领袖也。《刘玄传》:“三辅苦赤眉暴虐,皆怜更始,而张卬等以为虑,谓禄曰:‘今诸营长多欲篡圣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灭之道也。’”《刘盆子传》:“三辅郡县营长遣使贡献,兵士辄剽夺之。”何以知营长为宗族集团的领袖呢?《第五伦传》继前引伦筑壁之文后,续云:“伦始以营长诣郡尹鲜于褒。褒见而异之,署为吏。”《通鉴》卷四十胡三省注“三辅郡县营长遣使贡献”文云:“时三辅豪杰处处屯聚,各有营长。长、知两反。”可见营长确为民间宗族组织的领袖,而且已成一普遍的社会称号。这更反映出当时士族大姓的自卫营壁之多。
当兵革之际,士族大姓除筑营壁以防御寇贼外,同时也集体避难。《杜林传》:“王莽败,盗贼起,林与弟成及同郡范逡、孟翼等将细弱俱客河西。”《朱晖传》:“朱晖字文季,南阳宛人也。家世衣冠。晖早孤,有气决。年十三,王莽败,天下乱,与外氏家属从田间奔入宛城。道遇群贼,白刃劫诸妇女,略夺衣物。昆弟宾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动。晖拔剑前曰:‘财物皆可取耳,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晖死日也!’”而士族之家则至有携门生弟子同行者,如《承宫传》:“承宫……经典既明,乃归家教授。遭天下丧乱,遂将诸生避地汉中。”《桓荣传》:“莽败,天下乱。荣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虽常饥困而讲论不辍。”郭丹“既至京师,常为都讲,诸儒咸敬重之。大司马严尤请丹,辞病不就。王莽又征之,遂与诸生逃于北地”。(同书本传) 甚至在征战之中,宗亲细弱亦随在军营,如光武尝谓耿纯曰:“军营进退无常,卿宗族不可悉居军中。”乃以纯族人耿伋为蒲吾长,悉令将亲属居焉。(《耿纯传》) 邓禹亦谓张宗曰:“将军有亲弱在营,奈何不顾?”(《张宗传》) 又《东观汉记》卷十六载:“耿嵩字文都,巨鹿人。……王莽败,贼盗起,宗族在兵中。谷食贵,人民相食。宗家数百人升合分粮。时嵩年十二三,宗人少长咸共推之主禀给,莫不称平。”
(八)亲族之休戚相关
前面说过,士人与其宗族的关系,自武帝以后便日深一日。这种密切的宗族关系,在动乱之世表现得更为显著。此观当时起事者多以宗族为基础之事实即可了然。 而且在这种情形之下,宗族即有不参加者,事败亦不能免于祸。邓晨响应汉兵,及汉兵败退,“新野宰乃污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人入汤镬中?(按邓晨娶光武姊,故云) ’晨终无恨色”。(同书本传) 彭宠尝有大功于光武,后复叛之,事败遂“夷其宗族” 。隗嚣季父崔闻更始立,亦欲起兵应汉。嚣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听。”(同书本传,又《后汉纪》卷一) 赵孝王良为光武叔父,“光武兄弟少孤,良抚循甚笃。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曰:‘汝与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谋如是!’既而不得已,从军至小长安”。(同书本传) 盖当时整个宗族的祸福相依,无法分开,故族中主要人物的动向势必牵连及于全族。而族人为自身的利害计,最后亦唯有出诸支持一途。此所以刘良虽反对侄辈之举,终“不得已”而从军;隗嚣虽不赞成叔父之谋,也还是卷入了漩涡,且成为领袖人物也!
尤有进者,当时的宗族关系尚不止于一姓,父族之外,往往扩大至母族与妻族。地皇四年王莽诏已云:“刘伯升与其婚姻党与妄流言惑众,悖畔天命。”其后光武阵营中,如樊宏为“世祖之舅”,是母党;阴识、阴兴为阴后兄弟,是妻党;又如邓晨,自邓氏言亦为妻族。田戎据夷陵,其妻兄辛臣亦在军中,同为妻族之证。不仅此也,当时又有因争取宗族势力而交结婚姻者。早在王莽时,刘敞“欲结援树党,乃为祉娶高陵侯翟宣女为妻”(《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 。注引《东观记》曰:“敞为嫡子终娶宣子女习为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门,二十余日,义起兵也。”又延岑、田戎“并与秦丰合。丰俱以女妻之”。(同书《公孙述传》) 田戎已有妻室而秦丰犹以女妻之,其以婚姻为交结之手段,尤为明显 。更为明显的例子是光武娶郭后,《刘植传》载:“时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众十余万,世祖遣植说扬,扬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乃与扬及诸将置酒郭氏漆里舍,扬击筑为欢,因得进兵拔邯郸,从平河北。”从这一条证据看,光武之定河北实颇得力于婚姻关系。 鲍永“遣弟升及子婿张舒诱降涅城,舒家在上党,(田) 邑悉系之”(《冯衍传》) 。同传注引《东观汉记》载田邑致鲍永书曰:“张舒内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党,已收三族,将行其法。能逃不自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则妻党关系亦有凌驾乎本族之上者矣!
(九)不重单身之士
由于宗亲势力的浩大,故光武不甚重视单身的士人。只有背后附有宗亲势力者才能真正为光武所倚重。如邓晨“为常山太守,会王郎反,光武自蓟走信都。晨亦间行会于巨鹿下,自请从击邯郸。光武曰:‘伟卿以一身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归郡”。(《北堂书钞》七四引司马彪《续汉书》,又见范书本传) 鲍永知更始已亡,“悉罢兵,但幅巾与诸将及同心客百余人诣河内。帝见永,问曰:‘卿众何在?’永离席叩头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诚惭以其众幸富贵,故悉罢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悦。时攻怀未拔,帝谓永曰:‘我攻怀三日而兵不下,关东畏服卿,可且将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谏议大夫。至怀,乃说更始河内太守,于是开城而降。帝大喜。”注引《东观记》曰:“永说下怀,上大喜,与永对食。”(《鲍永传》) 光武这一不悦一大喜,充分地说明了背后没有势力的单身士人在那时确已无大作用。而当时士人中亦有知之者。光武召见冯异,异曰:“异一夫之用,不足为强弱。有老母在城中,愿归据五城,以效功报德。”(《冯异传》) 单身之士偶有被重用者也还是因为他有宗族的背景。岑彭荐韩歆于光武,“因言韩歆南阳大人,可以为用。’乃贳歆,以为邓禹军师”。李贤注曰:“大人,谓大家豪右。”又曰:“贳,宽也。”(《岑彭传》) 耿纯说李轶,“轶奇之,且以其巨鹿大姓,乃承制拜为骑都尉,授以节令,安集赵、魏”(《耿纯传》) 。
(十)光武集团与士族大姓的一般关系
以上许多分析已很明白地显示出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的关系如何深切。唯上引诸例证还只是个别性的,现在我们试再根据若干史料来说明东汉政权与士族大姓的一般关系。
光武兄弟初起时即得力于南阳士族大姓的拥戴,前已言之矣!《后汉书·王常传》亦云:“及诸将议立宗室,唯常与南阳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鲔、张卬等不听。”其后光武在河北亦因获得若干士族大姓的支持,始能击败王郎。光武交结刘扬兄弟之事固是一例,而尤要者则为上谷耿况父子与渔阳彭宠。《耿弇传》载:
弇因从光武北至蓟。闻邯郸兵方到,光武将欲南归,召官属计议。弇曰:“今兵从南来,不可南行。渔阳太守彭宠,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发此两郡,控弦万骑,邯郸不足虑也。”光武官属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后两郡兵俱来,光武见弇等,悦,曰:“当与渔阳、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我们于此可以注意到两点:1.光武集团到处交结士族大姓以建立根基。2.彭宠之从光武更显出当时士族大姓有浓厚的地域观念。
士族大姓之势力既遍布全国,而其所以起事或拥众自立,最初又多为保全宗族与财产。故任何集团如想获得政权,势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照顾到此一士族大姓阶层的社会经济利益。何况当时那些武装集团本身,如前面的分析所已指陈的,便主要是来自这个阶层呢?东汉政权之建立,和它在这一方面应付得比较适当,极有关系。《后汉纪》卷四载“建武四年”条下云:
鬲县五姓反,逐其守长。诸将曰:“朝击鬲,暮可拔也。”汉怒曰:“敢至鬲下者斩,使鬲反者,守长罪也。”移檄告郡牧守长,欲斩之。诸将皆窃言:“不击五姓,反欲斩守长乎?”汉乃使人谓五姓曰:“守长无状,复取五姓财物,与寇掠无异,今已收斩之矣!”五姓大喜,相率而降。诸将曰:“不战而下人之城,非众所及也!”(按《后汉书·吴汉传》注曰:“五姓盖当土强宗豪右也。”)
吴汉不攻五姓而杀守长,是因为守长侵犯了五姓的权利,而五姓之反亦确以此。吴汉的处置之所以成功,也正在于他把握到了东汉政权的本质。诸将但折于他能“不战而下人之城”,殊不知他的高明实在于政略而非战略也。还有一件极重要的事实也可以说明东汉政权与士族大姓之间的关系。《通鉴》卷四十“建武二年”条下云:
庚辰,悉封诸功臣为列侯。梁侯邓禹、广平侯吴汉皆食四县。博士丁恭议曰:“古者封诸侯不过百里,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四县,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也。”……帝令诸将各言所乐,皆占美县。(参看《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强干弱枝”原为西汉早期的重要政策之一,及至中叶以后,其事已颇松弛,然犹未被正式放弃。今光武政权之建立既颇有赖于士族大姓的助力 ,自不能再继续西汉初期那种抑止强宗豪族发展的政策。而且由于士族大姓业已遍布国中,传统的移徙政策事实上也无法再推行下去。丁恭之议真是太“不识时务”了!光武对当时的士族大姓如此迁就,而桓谭上疏犹云:“臣谭伏观陛下用兵,诸所降下,既无重赏以相恩诱,或至虏掠夺其财物,是以兵长渠率,各生狐疑,党辈连结,岁月不解。”(《后汉书》本传) 是希望光武对士族大姓的政策更为放宽也。但事实上一个要统一全国的政权与分散各地、拥兵自保的士族大姓之间多少是存在着矛盾的。这种矛盾,在战乱之际还不易察觉,等到局势稍一稳定,便自然地暴露出来了。兹举两事以说明之。
(建武)十六年……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稟,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自此以后东汉政权完全稳定。光武对于这些武装宗族采取了怀柔与分化并用的策略,直到完全摧毁了他们的力量才肯罢手。在这里,我们看到东汉政权建立最后所遭遇到的困难,仍在于士族大姓的拥兵自立,又据常璩《华阳国志》卷五:
建武十八年,刺史郡守抚恤失和。蜀郡史歆怨吴汉之残掠蜀也,拥郡自保。世祖以天下始平,民未忘兵,而歆唱之,事宜必克。复遣汉平蜀,多行诛戮。世祖诮让于汉,汉陈谢。
按吴汉这次之所以不能仿其降五姓之例,而光武也认为“事宜必克”者,实因天下初定,大姓拥兵自保之风不容再长,故不能不以武力镇压之。观《华阳国志》同卷载吴汉平公孙述后,立即“搜求隐逸,旌表忠义”。及汉诛戮过多,光武帝亦深责之,其交结蜀郡士族大姓之意,甚为显然也!
(十一)更始与赤眉败亡之社会背景的分析
到现在为止,本文仅讨论了两汉之际的群雄——尤其是光武集团,如何赖士族大姓的支持而建立基业的历史。但是另一方面,当时也有非士族大姓的集团,虽曾在军事上赢得一时的胜利,而终不免于覆亡者。其原因究竟何在呢?如果我们要彻底澄清此一时期政治变迁的社会背景,则不能不对此问题有一比较圆满的解答。这样,我们便须一察更始与赤眉两大集团的社会本质。
这两个集团起事很早,势力也一度极为浩大,而且均曾先后据长安,企图建立起全国性的统一政权,但结果都未能逃避失败的命运。这里我们无法涉及它们兴亡的全部经过与原因,而只能就其与本文题旨直接相关的地方略加分析而已。从它们社会根源与得势后的一般作风来看,我们至少可以找出下列三个最相同之点:1.饥民的乌合之众,故领袖人物多出身低微 ;2.流动性极大,且到处抢掠 ;3.缺乏良好的组织,故无力统治国家。兹分别论列于后。关于第一点:
更始 此集团系以新市、平林之兵为主体。《后汉书》云:“王莽末,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王凤为平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刘玄传》) 其为饥民毫无可疑。邓禹尝谓光武曰:“更始……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同书本传) 虽然此集团中亦有士族大姓势力,如光武兄弟所领导的一支,然远不敌原有集团的力量,故其间常有冲突与斗争。《后汉纪》卷一曰:“诸将请立君,南阳英雄(按范书《刘 縯传》作“豪杰”) 及王常皆投归伯升。然汉兵以新市、平林为本,其将帅起草野,苟乐放纵,无为国之略。皆惮伯升而狎圣公。”此所谓“英雄”、“豪杰”皆为士族大姓之流,故后“豪杰失望多不服”(《刘縯传》) 。我们于此实可窥见两派斗争之消息。更始本人出身宗室,其立场原与光武兄弟相去不远,然在诸将扶持下亦无可如何。伯升被诛,其咎亦不在更始,《刘縯传》载大会诸将事云:“更始取伯升宝剑视之,绣衣御史申屠建随献玉玦,更始竟不能发。”种种事实都说明更始集团确在下层阶级分子控制之下,更始处于其中,较之刘盆子之在赤眉集团,相去不过一间耳!明乎此,则光武虽悲兄之死而终不甚怨恨更始者,其故亦可得而明矣!
赤眉 此集团中包括分子也极复杂,虽有大姓如吕母之属,但通体而论,则仍为饥民集团。《汉书》云:“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饥馑相聚,起于琅邪,转钞掠,众皆万数。”(《王莽传下》) 《后汉书》则云:“时青徐大饥,寇贼蜂起,众盗以崇勇猛,皆附之。”(《刘盆子传》) 后在长安时杨音骂诸将曰:“诸卿皆老佣也!”即以其领袖樊崇而论,史称其“虽起勇力而为众所宗,然不知书数”。光武亦谓崇曰:“卿所谓铁中铮铮,佣中佼佼者也。”(均见同上) 故赤眉之为饥民集团及其领导者的出身微贱,早成定论,不烦详说。
关于第二点:
更始 新市、平林兵初起时即流窜抢掠,如“攻拔竟陵,转击云杜、安陆,多略妇女,还入绿林中”。其后因一度与士族大姓的势力相结合,欲成大事,稍为收敛,而积习终不能改。既至长安,“诸将后至者,更始问虏掠得几何,左右侍官皆宫省久吏,各惊相视”。后赤眉将至,张卬与诸将议曰:“赤眉近在郑、华阴间,旦暮且至。今独有长安,见灭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转攻所在,东归南阳,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复入湖池中为盗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为然。”(均见《后汉书·刘玄传》) 其流窜与掠夺的本质终于完全暴露出来了。故耿弇谓光武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诸将擅命于畿内,贵戚纵横于都中。天子之命,不出城门,所在牧守,辄自迁易,百姓不知所从,士人莫敢自安。掳掠财物,劫掠妇女,怀金玉者,至不生归。”(同书本传) 这一番话同时也说明了更始为诸将所挟持的真相。冯衍亦尝谓鲍永曰:“然而诸将虏掠,逆伦绝理,杀人父子,妻人妇女,燔其室屋,略其财产。”(同书本传) 冯异亦云:“今下江诸将,纵横恣意,所至虏掠财物,略人妇女。百姓已复失望,无所戴矣!”(《后汉纪》卷一) 其他有关记载尚多,不必尽录。
赤眉 赤眉初时流窜于东方,本皆“以困穷为寇,无攻城徇地之计”,及至长安建立政权,犹四处抢掠。故刘盆子说:“今设置县官而为贼如故。吏人贡献,辄见剽劫,流闻四方,莫不怨恨,不复信向。”虽一度徇盆子之求,“闭营自守,三辅翕然……百姓争还长安,市里且满,得二十余日”。可是紧接着“赤眉贪财物,复出大掠。城中粮食尽,遂收载珍宝,因纵大火烧宫室,引兵而西”。所以后来光武也对樊崇等说:“诸卿大为无道,所过皆夷灭老弱,溺社稷,污井灶。”(均见同书《刘盆子传》)
关于第三点:
更始 《后汉书·刘玄传》载:“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绣面衣、锦袴、襜褕、诸于,骂詈道中。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惠栋《补注》卷五曰:“《东观记》曰:‘更始在长安,官爵多群小,里闾语曰:使儿居市决,作者不能得,佣之市空返。问何故,曰:今日骑都尉注会日也。由是四方不复信向京师。’”《三辅旧事》曰:“‘更始遣将军李松攻王莽,屠儿卖饼者皆从之。屠儿杜虞手杀莽。’故其时所授官爵,皆屠沽之辈也。”《后汉纪》卷二载博士李淑谏更始之言曰:“陛下本因下江平林之势,假以成业,斯亦临时之宜。事定之后,宜厘改制度,更延英俊,以匡王国。今者公卿尚书皆戎阵亭长凡庸之隶,而当辅佐之任。”
赤眉 此集团无文书旌旗号令之事,前已言之,足见其缺乏组织的状态。后来他们仍然“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名为群贼”。还是接受了士人方阳(方望之弟) 的劝告,才立刘盆子为帝。兹再引《后汉书·刘盆子传》中的一段文字以说明其本质:“入长安城,更始来降。盆子居长乐宫,诸将日会论功,争言讙呼,拔剑击柱,不能相一。三辅郡县营长遣使贡献,兵士辄剽夺之。又数虏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复固守。至腊日,崇等乃设乐大会,盆子坐正殿,中黄门持兵在后,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笔书谒欲贺,其余不知书者起请之,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农杨音按剑骂曰:‘诸卿皆老佣也!今日设君臣之礼,反更殽乱,儿戏尚不如此,皆可格杀!’更相辩斗。”
以上三方面的大体比较,确可使我们相信,更始与赤眉两集团在社会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其起事与失败的原因也有根本相同之处。消极方面,他们的流窜与抢掠损害了士族大姓的利益;积极方面,他们缺乏文化修养与组织才能,更无法满足新兴的士族大姓阶层之政治要求。以毫无社会基础的乌合之众而与全国最有势力的士族大姓阶层为敌,在当时的情形下,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我们今天尽管同情他们的社会处境,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使他们走向覆亡之途的历史条件。而我们对于这两大集团的分析,更从反面指出了一项原则,即当时不能得到士族大姓阶层普遍支持的集团,虽有强大的武力,也是很难存在的。
(十二)略论士族化程度与政治成败的关联
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饥民集团在推翻旧秩序上,是有其一定的作用的。王莽政权的崩溃以及东汉政权的建立,上述两大集团确曾尽了开路之功。然而他们的功能也仅止于此——可以除旧,不足以布新。原因何在呢?这就不是社会经济基础这一简单事实可以完全解释得清楚的了。从本文的整个讨论来看,文化程度的深浅对于政治变迁的影响,无疑也极为重要。
(十三)从士大夫名称之演变看东汉政权的社会背景
更始三年(亦建武元年) 春,光武还只是萧王,在一连串的军事胜利后,诸将都一致议上尊号,请求光武自立为帝,一连三次都为光武严词拒绝。《后汉书·光武帝纪》(《后汉纪》卷三、《通鉴》卷四十略同) 载:
光武曰:“……诸将且出。”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纯言甚诚切,光武深感,曰:“吾将思之。”
这一段事实极值得我们注意者有数点:1.光武不肯立即登帝位,决非虚伪做作,实因当时形势犹未稳定,而他本人又是一向深谋远虑,不敢轻举妄动的。2.诸将再劝请上尊号亦确极诚恳,因为诚如耿纯所说,这和他们本身的利害是密切相关的。3.光武不顾诸将之请而独感于耿纯之论,也并不仅是由于“纯言甚诚切”,更重要的,乃是耿纯当众明白地指出了光武集团中人结合的真正因素与关键。因之,如果光武再不加考虑,则确不免会影响到“攀龙附凤”者的团结精神。 4.耿纯屡用“天下士大夫”这个名词,又谓“捐亲戚、弃土壤”,是已说明在当时追随光武者之中,极多士族大姓。了解了这一点,旧籍中有许多骤看似无深意的老话,在此便都发生了新的意义。《后汉纪》卷一光武对王霸说:“梦想贤士共成功业,岂有二哉!”同书卷二(又见《后汉书·景丹传》) 谓耿弇等曰:“方与士大夫共此功名耳!”同书卷四载桓谭于建武四年上疏有云:“陛下若能轻爵禄,与士大夫共之,而勿爱惜,则何招而不至,何说而不释,何向而不闻,何征而不克。”(又《后汉书·桓谭传》作“轻爵重赏,与士共之”) 《后汉书·王常传》亦云:“唯常与南阳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同书《岑彭传》载彭说光武曰:“窃闻大王平河北,开王业,此诚皇天佑汉,士人之福也!”以“汉”与“士人”并举,便可见光武政权与士族大姓之休戚相关。而士族大姓对王权的“攀龙附凤”,也是当时士大夫的一个普遍意识。《后汉书·寇恂传》:“恂与门下掾共说耿况曰:‘……今闻大司马刘公,伯升母弟,尊贤下士,士多归之,可攀附也。’”
为使问题更为清楚起见,我们在此必须略有追溯“士大夫”一词在两汉时意义的变迁。“士大夫”这个名词古已有之,盖从封建制度中的“大夫”与“士”两称号逐渐演变而成。《史记》、《汉书》中均常见“士大夫”之字样,唯《汉书》系东汉人手笔,班固著史时,其所用名词,可能已渗入当时社会所流行的意义。故为谨慎计,我们先看《史记》中的“士大夫”。
《史记》中的士大夫,主要是指武人(军官) 而言,所以屡见于武将列传。韩信背水破赵,诸将问其故。“信曰:‘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淮阴侯列传》) 同传广武君谓信曰:“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醳兵。”李广自杀,“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又太史公曰:“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李将军列传》) 武帝使司马相如作檄告巴蜀民曰:“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伍被谓淮南王曰:“大将军(卫青) 遇士大夫有礼,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之用。”(《淮南衡山列传》) 武帝曰:“纵单于不可得,(王) 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以得慰士大夫心。”(《韩长孺列传》) 文帝元年诏亦有“高祖亲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孝文本纪》) 。这里“士大夫”一词都很明显地是指着武人而言。这一意义的“士大夫”亦保存于《汉书》之中。胡建既斩监军御史,上奏有云:“不立刚毅之心、勇猛之节,亡以帅先士大夫。”(《胡建传》) 元帝劳冯奉世诏亦云:“故遣将军帅士大夫行天诛。”(《冯奉世传》) 又司马迁《报任安书》曰:“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司马迁传》)
《史记》中也有含义较广的“士大夫”,然有时分作两词,非如后世之合而为一。袁盎谓申屠嘉曰:“且陛下从代来,每朝,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尝不称善。何也?则欲以致天下贤士大夫。”(《袁盎晁错列传》) “张汤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酷吏列传》) 又《游侠列传》郭解曰:“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 尤其清楚的是下面一段文字。《卫将军骠骑列传》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索隐》:谓不为贤士大夫所称誉) ,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在这一段话里,我们一方面看到“士大夫”已有较广泛的社会含义,而另一方面则可以断言,《史记》中之士与大夫在有些处确不可分开。这一类的“士大夫”,《汉书》中更是数见不鲜。汉高祖十一年诏曾数“贤士大夫”字样,其文曰: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高祖纪下》)
我们试将此诏所流露的傲慢之气,与前引耿纯说光武之情味作一比较,便立即可以看出“士大夫”在两汉政权建立之初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及其在统治者心目中的轻重之别。尤其是“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以及“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等语,最足以显出那时的“士大夫”对统治者的片面依赖性。再就其十二年封功臣诏中所谓“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之言推之,则其时“士大夫”主要是指与高祖共同打天下的文武功臣而言的。而“士”与“大夫”两个名词之可以分开,并被个别的冠以“贤”、“豪”之类的形容词,也极为明显。另一方面,《汉书》中又已有了专门社会名词的“士大夫”。武帝元朔三年诏即有“与士大夫日新”之语,元封元年复云“与士大夫更始”。(均见《孝武纪》。又《史记》褚少孙《补孝武本纪》,亦有“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之言。按少孙为元、成间人,已在西汉下叶矣!) 此后这一类的话遂屡见于两汉诏书之中,不烦详引。崔寔《政论》谓汉代:“践祚改元际……每其令曰:‘荡涤旧恶,将与士大夫更始。’”(《群书治要》卷四十五引) 诚是也!不但诏书中常用“士大夫”一词,一般社会上似亦通用此称号。兹再举数例于下(按前文已引者从略) :宣帝时韦玄成“素有名声,士大夫多疑其欲让爵辟兄者”(《韦贤传》) 。元帝时朱博“随从士大夫,不避风雨”(《朱博传》) 。成帝时胡常“居士大夫之间,未尝不称述方进”(《翟方进传》) 。
从上面这一番检讨中,我们知道,“士大夫”在汉初时主要系指武人,但愈往后便愈具有较广的社会含义。虽然后来的史籍中亦多少保存了一些“士大夫”的早期用法。我们把这种观念的演变配合着实际的社会变迁来看,才能明白其所以有此演变之故。这更加深了我们对于西汉社会士族化过程的理解。由此可见,“士大夫”一词从汉初到士族兴起以后,在内容上确已起了很大的变化。谨慎一点说,至少在东汉政权建立之际,它已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士大夫阶层”之意义。因之,此所谓“士大夫”,自不仅限于追随光武起事的少数功臣,而可以在概念上将士族、大姓、官僚、缙绅、豪右、强宗……等等不同的社会称号统一起来,尽管这些人的社会成分在大同之中仍存在着小异。而我们更可由此一含义的“士大夫”名称之成立,了解到士族在当时社会上,尤其占有主导性质的事实。
如果我们对“士大夫”的分析是正确的,则不仅东汉政权赖之而建,即光武以下诸功臣的勋业亦依之而立。《后汉书·寇恂传》:“恂经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从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独享之乎!’时人归其长者,以为有宰相器。”同书《马援传》:“‘今赖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诸君纡佩金紫,且喜且惭。’吏士皆伏称万岁。”(又略见《后汉纪》卷七) 又同书《来歙传》:“歙为人有信义,言行不违;及往来游说,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从之,多为其言,故得免而东归。”(按时歙为光武使于隗嚣,嚣尝欲杀之。) 又邓训“乐施下士,士大夫多归之”(同书《邓禹传》) 。杜林“京师士大夫咸推其博洽”(同书本传) 。“士大夫”在当时已是一广泛的社会称号,观此益信。
(十四)结语
本文的全面分析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东汉政权的建立实以士族大姓为其社会基础。光武集团之所以能在群雄并起的形势下获得最后的胜利,除了刘秀个人的身世 ,及其所处的客观环境较为有利外,它和士族大姓之间取得了更大的协调,显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关于东汉政权与一般大姓之间的关系,近代学者已早有所论列 。本文虽亦颇有涉及一般大姓之处,然其主旨则在企图更进一步地指出士族势力对于两汉之际政治变迁的特殊影响。唯因当时的士族与大姓在广泛的社会经济立场上是相当一致的,故有时遂不能不合并讨论之。盖以旧史记载多语焉不详,除少数情形外,要想把士族与大姓截然分开,的确已很为困难。但并不是说,这二者是没有分别的。就本文的整个讨论言,其间的分别固已甚为明显:它们在一般社会经济基础上的共同点掩盖不了它们在文化程度上的差异。而这差异则正是决定着光武集团崛起于群雄之间的关键。不可否认,士族在当时社会上确实特别起着主导的作用,那就是说,在这一阶段的历史进程中,不是士族跟着大姓走,而是大姓跟着士族走。这一论断,至少就作者目前的了解,是铁案难移。光武能尊重天下隐者如周党、严光之流,而公孙述不能容巴蜀一地的不仕之士,仅此一端便可知光武的成功,自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绝不是偶然的。范蔚宗在《卓茂传》论里曾给我们透露出一点消息:
建武之初,雄豪方扰,虓呼者连响,婴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给之日。卓茂断断小宰,无它庸能,时已七十余矣,而首加聘命,优辞重礼,其与周、燕之君表闾立馆何异哉?于是蕴愤归道之宾,越关阻,捐宗族,以排金门者,众矣。
而汉末傅干在《王命叙》中则明白地指出:
且世祖之兴有四:一曰帝皇之正统,二曰形相多异表,三曰体文而知武,四曰履信而好士。……言语、政事、文学之士咸尽其材,致之宰相;权勇毕力于征伐,绅悉心于左右。此其所以成大业也!(《艺文类聚》十引,又见《全后汉文》八十一)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东汉王朝完全是代表士族大姓利益的政权,历史的发展固非任何单一因素所能完全解释的。东汉中叶以后(和帝以下) 的历史,便逐渐显示出此政权在本质上与士大夫阶层确有矛盾之处。由此种种矛盾而产生的士族势力与王室势力的全面冲突,充满了此后的东汉史,我们在此已不能涉及。我们在此应说的是,此一借着士族大姓的辅助而建立起来的政权,最后还是因为与士大夫阶层之间失去了协调而归于灭亡。
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引言
近世以来,中外学者考论魏晋士族发展与清谈思想者亦已多矣。窃不自量,尚欲于此有所申述,聊以补诸家之所未及,此兹篇之所以作也。盖时贤之用心,或偏重于士族政治、经济势力之成长,或深入于清谈之政治背景之隐微,要多为分析之作,而鲜有综贯之论。斯篇主旨以士之自觉为一贯之线索而解释汉晋之思想变迁。窃谓依此解释,不仅儒学之变为老庄,其故可得而益明,即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之变动而最为近人所措意者,亦未尝不可连贯而参证之。故本文但求立己,不求破人;至于所涉诸端而或有为前修时彦所已发者,则但力求就知解所及而采择融会之,借示崇敬之微意焉!
(一) 士之群体自觉
从私谥之事可推知当时士大夫群体自觉之观念并不限于与其他社会集团相区别之士大夫集团一层,而已进而发展为内在之分化。盖门生弟子既各推尊其师,则群体自觉亦必存在于各家之间,可不待论矣!东汉部党始于甘陵南北部,史言二家宾客互相讥揣,又各树朋徒,遂渐成尤隙,此即党事之兴与门生弟子之各推尊其师有关之显证。至于南北部之名则又显示士大夫之地域分化,为当时士之内在分化之一重要层面,不可不略加讨论者也。
……
除地域之分化外,士大夫复有上层与下层之分化。而所谓上层与下层之分化者,其初犹以德行为划分之标准,稍后则演为世族与寒门之对峙,而开南北朝华素悬隔之局,故尤不能不略加考释也。
(二) 士之个体自觉
论汉晋之际士大夫与其思想之变迁者,固不可不注意士之群体自觉,而其尤重要者则为个体之自觉,以其与新思潮之兴起最直接相关故也。然群体自觉之背景不明,则个体自觉之源流不畅,兹考释群体自觉既竟,乃及于个体自觉焉!
……
按:士大夫重生前与身后之名,正是个体自觉高度发展之结果。盖人必珍视其一己之精神存在而求其扩大与延绵,然后始知名之重要。若夫在重集体之社会中,个体自觉为大群体之意识所压缩,所谓“一切荣誉归于上帝”者,则个人之荣辱固无足措意也。14世纪之意大利亦以个体自觉著称。其时最负盛名之文士彼特拉克(Petrach) 者,早岁慕俗世之荣名,晚年意境不同,著《致后世人书》,道其渴望名垂不朽之至意。近人论西方个人意识之源流者多引彼氏为先例,此亦重视名之价值为个体自觉外在表现之一端,而足资参证者也。
……
士大夫之内心自觉复可征之于对个体自我之生命与精神之珍视。《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传》曰:
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骘闻融名,召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应命,客于凉州武都、汉阳界中。会羌虏飚起,边方扰乱,米谷踊贵,自关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
此种“生贵于天下”之个人主义人生观,正是士大夫具内心自觉之显证,毋须更有所解说也! 同书卷八十下《文苑列传下·张升传》曰:
升少好学,多关览而任情不羁。其意相合者,则倾身交结,不问穷贱;如乖其志好者,虽王公大人,终不屈从(按:可参照上篇论同志条所引《刘陶传》之文)。常叹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有知我,虽胡越可亲;苟不相识,从物何益?”
按:任情不羁,唯一己之好尚是从,皆是极端以自我为中心之思想,亦足为内心自觉之具体说明也。
(三) 汉晋之际新思潮之发展
上两节中既陈士之自觉甚详,兹请进而略论其时之思想变迁。唯平章学术,其事至为不易,非作者之力所敢承,且限于篇幅,势亦不能于汉晋间之学术思想为全面之评述。故所论将仅及发展之大势,而复以足与前两节之旨互相发明者为断,或者可于考镜源流一端略有助益欤?
《颜氏家训》卷三《勉学》篇曰:
学之兴废,随世轻重。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宏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来不复尔。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曰:
汉师拘虚迂阔之义,已为世人所厌。势激而迁,则去滞著而上襄玄远。
按:儒家经术之衰与老庄思想之兴最为汉晋间学术思想变迁之大事。此一转变之原因虽甚多,要可自两方面言之。一为客观方面之原因:汉人通经所以致用,今经学末流既不能施之世务,则其势乃不得不衰,此颜氏之论也。一为主观方面之原因:一种学术思想之流行除因其具实用之价值外,又必须能满足学者之内心要求。而汉儒说经既羼以阴阳五行之论,复流于章句烦琐之途,东京以降遂渐不足以厌切人心,其为人所厌弃则尤是事有必至,此吴氏之说也。本篇仅就士之自觉之背景考察思想之变迁,故所涉不出主观方面之范围,而置客观之因素不论焉!
汉魏之际儒学渐衰,近人颇有论及之者。 兹先就章句式微之事实,以说明思想转变之趋向。章句之烦琐,西汉已然,降及东京,其风弥甚。
……
以上论东汉中叶以后儒学之发展,自马、郑以至荆州,皆以鄙章句之烦琐而重经典之本义,为其间一贯线索。其流变所及则渐启舍离具体事象而求根本原理之风,正始玄音乃承之而起,此学术思想将变之候也。汉魏之际,延笃、曹植有《仁孝论》,朱穆有《崇厚绝交论》,刘梁有《破群论》、《和同论》,虽思想不出儒家之范围,其舍事象而言原理,则已开魏晋论文之先河。 汉末儒学弃末流之繁而归于本义之约,其事虽人所习知,但其所以有此转变之故,则尚有待于进一步探究。窃以为一切从外在事态之变迁而迂曲为说者,皆不及用士之内心自觉一点为之解释之确切而直截。盖随士大夫内心自觉而来者为思想之解放与精神之自由,如是则自不能满足于章句之支离破碎,而必求于义理之本有统一性之了解。此实为获得充分发展与具有高度自觉之精神个体。要求认识宇宙人生之根本意义,以安顿其心灵之必然归趋也。故东汉学术自中叶以降,下迄魏晋玄学之兴,实用之意味日淡,而满足内心要求之色彩日浓。跌宕放言之辈如孔文举、祢正平、嵇叔夜之罹祸虽多少皆与其思想有关,然卒不之顾,其重内心而轻外物之精神为何如耶!此亦汉晋之际学术思想之发展不得纯以政治状况等外在事态释之之故也。
……
今欲知儒学之所以衰,不能不知儒学在汉代社会文化上之功用。范蔚宗《后汉书·儒林列传》论曰: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夫书理无二,义归有宗,而硕学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自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暨乎剥桡自极,人神数尽,然后群英乘其运,世德终其祚。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
同书卷六十六《陈蕃传》(参考卷六十一末“蔚宗之论”) 论曰:
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险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絜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际会,协策窦武,自谓万世一遇也。懔懔乎伊、望之业矣!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按:蔚宗所论儒学之效用极为精当,其史识之卓越,诚不易企及。据此则儒学实与汉代一统之局相维系,儒学之功能在此,其所以终于蹶而莫能振者亦在此。盖自东汉中叶以来,士大夫之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日臻成熟,党锢狱后,士大夫与阉宦阶级相对抗之精神既渐趋消失,其内在团结之意态亦随之松弛,而转图所以保家全身之计,朱子所谓“刚大方直之气,折于凶虐之余,而渐图所以全身就事之计”者,诚是也。自此以往,道术既为天下裂,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之精神逐渐为家族与个人之意识所淹没。徐孺子寄语郭林宗:“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即是士大夫不复以国家或社会为念之证。蔚宗谓“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得其情矣。自党锢以后下迄曹魏,就士大夫之意识言,殆为大群体精神逐步萎缩而个人精神生活之领域逐步扩大之历程。 当时社会上最具势力之士大夫阶层既不复以国家社会为重,而各自发展与扩大其私生活之领域,则汉代一统之局势已不得不坠。 一统之局既坠,则与之相维系之儒学遂失其效用,而亦不得不衰矣。故推原溯始,儒学之衰,实为士大夫自觉发展所必有之结局。
明乎儒学之所以衰,然后始可与论玄学之所由兴。青木正儿氏论清谈思想之萌芽,采武内义雄之说,谓儒学沉溺训诂拘泥末节之弊至魏明帝太和、青龙之际为最甚,而清谈适起于此时,此二现象之因果关系可以推测云。 此说自今日观之,已不足信。盖儒学章句烦琐之弊,早在东汉中叶已为治经者所不满,其后郑玄以至荆州学派之简化运动即承此要求而起,前文已论及之。王弼注易又复承此一运动而更进一步探求宇宙万物之根本原理,遂牵连及于老子,通儒道而为一。故自学术思想之发展阶段言,玄学之兴起乃是汉末以来士大夫探求抽象原理之最后归趋。儒学之重心在人伦日用,形而上之本体本非所重,故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汉末经学之简化运动,充量至极,亦仅能阐明群经之大义,而不能于宇宙万物之最高原理提出“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之解答,此在魏晋之士则犹以为未达一间,而无以满足其内心深处之需求也。
……
是其明证,是以魏晋以下纯学术性之儒学虽未尝中断,而以经国济世或利禄为目的之儒教则确然已衰。 士大夫于如何维系社会大群体之统一与稳定既不甚关切,其所萦怀者遂唯在士大夫阶层及士大夫个体之社会存在问题。就此一角度言,魏晋思想之演变,实环绕士大夫之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而进行。盖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并不能常融合无间,其间颇有冲突抵触之事。如何消解此类冲突而使群己关系获致协调,遂为思想家所不能不注意之一中心问题。而对同一问题之不同答案,则形成流派之根本原因所在也。
……
论魏晋思想者常好言儒道之分合问题。实则以儒道分别流派,其间颇多扞格难通之处,殆未能触及其根本症结之所在也。就本文所已指陈者观之,则所谓儒,大体指重群体纲纪而言,所谓道,则指重个体自由而言。故与其用儒道之名而多所凿枘,何如采群己之分而更可发古人之真态乎?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者也。所谓个体之自由或道家,其事易了,而所谓群体之纲纪或儒学,则犹略有可说者。自汉代一统之局既坏,而儒学遂衰,此义前已论及之矣。但此特就汉代儒学经国济世之本质而言耳!而儒学之为物,下可以修身齐家,上可以治国平天下,因未尝拘于一格也。汉社既屋,经国之儒学乃失其社会文化之效用;而宋明理学以前,儒家性命之学未弘,故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资,老释二家亦夺孔孟之席。唯独齐家之儒学,自两汉下迄近世,纲维吾国社会者越二千年,固未尝中断也。而魏晋南北朝则尤为以家族为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而然耳!沈壵《落颿楼文集》卷八《与张渊甫书》有云:
六朝人礼学极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异于古之宗法,然与古不相远。史传中所载多礼家精粹之言。……古人于亲亲中寓贵贵之意,宗法与封建相维,诸侯世国,则有封建;大夫世家,则有宗法。
诚一针见血之论也。明乎此,然后乃知魏晋南北朝之所谓群体纲纪实仅限于以家族为本位之士大夫阶层,而不及于整个社会。何曾语司马昭之言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自来论者皆以司马氏篡曹魏之业,不能倡忠德,遂独标一孝字。斯言是矣,而殊未能尽。盖与汉代一统之局相维系之儒学既不复为士大夫所重,忠德固已失去社会号召力,而唯有倡孝道始能动人之心,以其最为士大夫群体纲纪之维持所需要故也。故六朝礼学虽精,其施用于朝廷之仪礼犹为虚文,唯纲维士大夫上层社会之礼法始具实效耳!《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黄汝成《集释》引杨编修(绳武) 之言曰:
六朝风气论者以为浮薄,败名俭,伤风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实复有不可及者数事,曰:尊严家讳也,矜尚门地也,慎重婚姻也,区别流品也,主持清议也。盖当时士大夫虽祖尚玄虚,师心放达,而以名节相高,风义自矢者,咸得径行其志。至于冗末之品,凡琐之材,虽有陶猗之赀,不敢妄参乎时彦;虽有董邓之宠,不敢肆志于清流。而朝议之所不及,乡评巷议犹足倚以为轻重。故虽居偏安之区,当陆沉之后,而人心国势犹有与立,未必非此数者补救之功,维持之效也。
按:文叔所言,其关涉道德判断者,于此可以不论,然本文所论群体纲纪与个体自由之分际则胥可本是而观之。六朝门第社会之纲纪诚赖此数事而立,然其所以卒至偏安陆沉者亦未始不与此有关也。
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
从3世纪初叶汉代统一帝国的终结到4世纪初叶南北分裂的开始这一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的时代。关于这一转变,中外史学家的论著多至不可胜计。在这许多现代讨论之中,魏晋士风曾是一个特别受到注目的问题。所谓士风,牵涉到两个不可截然划分的方面:一是知识分子(当时称之为“士”或“士大夫”) 的思想,一是他们的行为。就思想言,其特色是易、老、庄的三玄之学代替了汉代的经学;就行为言,其特色则是突破传统礼教的藩篱而形成一种“任诞”的风气。关于这一新士风的兴起和发展,从来的解释都着眼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一般背景方面。其中,尤以政治的背景最受史学家的注意,即所谓“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这一论断,大体说来,是有坚强的根据的。
但是魏晋士风的发展并不是单从外缘方面所能完全解释得清楚的。我在旧作《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中曾试图用“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的观念说明这个时代的知识阶层在内心方面所发生的种种变化。该文不是对传统的解释加以否定,而是想在传统的解释之外增添一个理解的层面。 但是该文断代仅止于西晋之初,对汉末以来名教崩溃的整个过程尚嫌语焉不详;至于东晋以后门第社会新秩序的重建,因限于体例,则完全没有谈到。本文对该文的论点有进一步的发展,取材则详略互见,所以基本上本文是该文的一个续篇,希望读者兼观并览。
(一)何谓名教
魏晋士风的演变,用传统的史学名词说,是环绕着名教与自然的问题而进行的。在思想史上,这是儒家和道家互相激荡的一段过程。老庄重自然,对当时的个体解放有推波助澜之力;周孔重名教,其功效在维持群体的秩序。概括地说,魏晋思想史可以分为三个小段落:曹魏的正始时代(240~248) ,名教与自然的问题在思想史上正式出现,何晏、王弼是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嵇康(223~262) 、阮籍(210~263) 等所谓“竹林七贤”代表名教与自然正面冲突的时代,而以嵇康被杀为其终点。西晋统一以后,名教与自然则转入调和的阶段,其理论上的表现则有郭象的《庄子注》(在惠帝时,290~306年) 和裴頠的《崇有论》(约撰于297年) 。下文讨论士风的演变是和这一思想史的分期密切相关的。
……
事实上魏晋所谓“名教”乃泛指整个人伦秩序而言,其中君臣与父子两伦更被看作全部秩序的基础。不但如此,由于门第势力的不断扩大,父子之伦(即家族秩序) 在理论上尤超乎君臣之伦(即政治秩序) 之上,成为基础的基础了。这一点,袁宏(328~376) 的史论足资证明。袁宏说: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
袁氏首先说明“君臣父子”是“名教之本”,接着又强调“君臣”关系是仿效“父子”关系而来的,可见东晋时代士大夫是把家族秩序放在比政治秩序更为基本的位置上(至于“贵贱”法“天地高下”之说,则显然是为当时门第社会的阶级制度作辩护) 。所以我们如果对“名教”一词采取广义的看法,则东晋以后的清谈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决不可视为“纸上空文”,这一点后文还会谈到。现在让我们先从广义的观点分析一下汉末以来的名教危机。
(二)君臣关系的危机
当时的名教危机在君臣一伦上的确表现得最为突出。汉代去古代“封建”之世不远,地方官(如郡守) 和他所辟用的僚属之间本来就有一种君臣的名分。东汉以后更由于察举制的长期推行,门生与举主之间也同样有君臣之义。这些所谓“门生故吏”便形成了门第的社会基础。这些士人在未直接受命于朝廷之前,只是地方长官或举主的臣下,而不是“天子之臣”。即使以后进身于朝廷,依当时的道德观念,他们仍然要忠于“故主”。 因此一般士人之于皇帝最多只有一种间接的君臣观念,但并不必然有实质的君臣关系。
……
《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传·汉阴老父传》说:
汉阴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有老父独耕不辍。尚书郎南阳张温异之,使问曰:“人皆来观,老父独不辍,何也?”老父笑而不对。温下道百步自与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温大惭,问其姓名,不告而去。
据同书卷七《桓帝本纪》,帝于延熹七年(164年) 十月戊辰幸云梦,临汉水。所以这故事的真实性很高,未必是后人造出来的。汉阴老父对张温用“今子之君”的称呼,足见他根本不承认和桓帝有任何“君臣之义”。至于他质问张温的几句话更开了魏晋以下君主观的先声。嵇康《答难养生论》曰:
且圣人宝位,以富贵为崇高者,盖谓人君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无主而存,主不能无尊而立。故为天下而尊君位,不为一人而重富贵也……圣人不得已而临天下,以万物为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与天下同于自得。穆然以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虽居君位,飨万国,恬若素士接宾客也。虽建龙旂,服华衮,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于上,烝民家足于下。岂劝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
在理论层次上,嵇康的话当然比汉阴老父敷陈得完备多了,但二者在思想基调上则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不妨说,正因为自汉末以来,社会上已流行着汉阴老父的那种议论,这才会逼出嵇康对君臣关系重新作有系统的反省。而先秦某些旧说,包括老庄在内,这时也就发生了新的现实意义。
这种对君职的怀疑观点再向前发展一步便成为阮籍和鲍敬言的无君论了。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说道:
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
阮氏首倡无君之论在思想上自然比汉阴老父为激烈。可是他的立论的主要根据依然是汉阴老父所指责的“役天下以奉天子”和天子的“劳人自纵,逸游无忌”。所不同者,2世纪的汉阴老父还相信有“昔圣王宰世”之事,而3世纪的阮籍由于经历了曹丕禅让的一幕,不免有“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的感触,因此对古代圣王也失去了信心。4世纪初的鲍敬言发挥“古者无君,胜于今世”的学说,提出了更多的论据。但论及有君之害,他最强调的也还是百姓更困和天下更乱,这一方面,和汉阴老父的说法先后呼应。
我们并不能说汉阴老父的思想对嵇康、阮籍、鲍敬言等人有什么影响。这里所要说明的只是从汉末到西晋这一百多年期间,名教中的君臣一伦已根本动摇了。在4世纪的初叶像鲍敬言这种无君论的思想一定相当流行,所以郭象注《庄子》特别加以驳斥。《人间世》“臣之事君义也”注说:
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不乱则散。故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
又《胠匣》“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注说:
信哉斯言。斯言虽信,而犹不可亡圣者,犹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须圣道以镇之也。群知不亡而独亡圣知,则天下之害又多于有圣矣。然则有圣之害虽多,犹愈于亡圣之无治也。
这些注语颇与葛洪驳鲍敬言的议论相通,不过有简繁之别、玄质之异而已。如果不了解当时思想的背景,我们不免要误会郭注是无的放矢了。像“无贤不可以无君”、“犹愈于亡圣之无治”这些话,其时代痕迹和驳论对象都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郭象虽然主张有君,却并无意恢复汉代的政治秩序,因为他所提倡的君道不但是无为的,而且还是“各任其自为”的,即是使士大夫都能“适性逍遥”的一种局面。所以西晋以下与自然合而为一的名教,其含义早已暗中偷换。名教的重点已从大一统的政治秩序转到高门华胄的家族伦理方面来了。
(三)家族伦理的危机
汉末以来名教的危机是全面性的,不限于君臣一伦,这一点葛洪曾给我们提供了很生动的资料。《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五《疾谬》说:
汉之末世……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以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类味之游,莫切切进德,訚訚修业,攻过弼违,讲道精业。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掣拨淼折,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尔者为劣。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诬引老、庄,贵于率任。大行不顾细礼,至人不拘检括。啸傲纵逸,谓之体道。呜呼惜乎,岂不哀哉!
同书外篇卷二十七《刺骄》说:
闻之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骄慢傲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弊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
首先必须指出,葛洪虽指明这些是汉末的社会现象,但事实上恐怕不免把他自己所见的士风时习也包括进去了,不过这种风气可以溯源至汉末是不成问题的。像葛洪所描写的这些行为显然不能认为完全是由政治情况造成的,而毋宁是个性解放后精神上要求打破一切桎梏的具体表现。葛洪骂他们“背叛礼教”,是不错的。魏晋时代的“礼教”或“礼法”主要是指在家族伦理的基础上所发展出来的一套繁文缛节。虽然在很多情形下,“礼教”或“礼法”也可以视为“名教”的同义语,但是前者的政治含义较轻而社会含义则较重。换句话说,“礼教”或“礼法”往往不是指着君臣一伦而言的。“名教”一词则比较笼统,有时可以解释为政治上的名分,就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汉末以来,史籍上所载的“背叛礼教”或“不遵礼法”之士,其实是对名教作全面性的反抗,其中包括然而绝不限于君臣一伦。嵇康在《难自然好学论》(《嵇康集》卷七) 中对这一点说得最清楚:
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
他们既认定六经礼律都是抑性犯情的,则不但君臣之伦要打破,其他一切人伦关系的价值也都不能不重新估定了。
我们先看看父子一伦。《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载:
(融)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这种议论,从字面上说,当然是从王充《论衡》中得来的。王充的《论衡·物势》篇说:
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子生矣。且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
但是往深一层看,两者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则截然不同。王充在这里是用“夫妇不故生子”的论证来打破当时儒者“天地故生人”的命题的,他似乎并没有再进一步去考虑“夫妇不故生子”这一论证的本身所可导致的逻辑结论。孔融则完全撇开了“天地故生人”的问题,而直接把“夫妇不故生子”当作一项经验事实来看待,并进而分析其中所涵蕴的父子关系。因为孔融所要破斥的不是目的论,而是世俗流行的关于“孝”的价值论。《论衡》在汉晋之际所发生的在思想上的影响往往都经过这样一层转折。 在王充的时代(1世纪) ,名教的危机还没有出现,《论衡》的主旨也绝不在“反叛礼教”。当汉末名教全面动摇之际,由于《论衡》中的许多论点恰好适合反礼法之士的需要,其书才大行其道,成为“谈助”。所以严格地说,王充只是给魏晋反礼法的运动提供了一些思想原料而已。至于正式对“孝”的理论提出非难,则始作俑者恐非孔融、祢衡莫属了。
孔融(153~208) 所经历的时代正值儒家的名教或礼法流入高度形式化、虚伪化的阶段。一部分由于察举制度的刺激,“累世同居”的大家族在士大夫阶层中逐渐发展起来了。 许多人为了博“孝”之名以为进身之阶,便不惜从事种种不近人情的伪饰,以致把儒家的礼法推向与它原意相反的境地。我们只要举一两个例证便足以说明这种情况。陈蕃任青州乐安太守时,
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遂致其罪。
陈蕃死在168年,正与孔融时代相衔接。孔融本人也可能有过和陈蕃类似的经验,据说他在北海相任内,“有遭父丧,哭泣墓侧,色无憔悴”,他就把这个伪孝子杀了。 这个故事不一定可信,但足以说明当时伪礼教的盛行。葛洪记汉末的谚语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 这更说明了当时的伪孝和察举制度之间的密切关系。又如兄弟让财也是东汉的一种风气,有“让”名的人往往可以获得地方官的荐举。但应劭在《过誉》篇中就指出其虚伪性,并感叹道:“凡同居,上也;通有无,次也;让,其下耳。” 应劭是2世纪末叶人,他的话更可以使我们认识孔融“非孝”的背景。而且综合葛洪和应劭的记载,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在“累世同居”大家族的发展阶段,其中已隐藏着一种“分居”的倾向。
上引孔融、祢衡两人关于“父之于子,当有何亲”的一番问答,据《后汉书》所言,本是出于路粹的“枉奏”,即经过了恶意的歪曲。其实孔融并不“非孝”,他是怀疑“孝”是否如世俗所言,仅仅建立在生物的事实之上而已。《后汉书》本传上明说他“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可见他内心的矛盾起于当时虚伪礼法和真正的父子之情不能相应。在这一点上,他是开魏晋士风的人物之一。《后汉书》卷八十三《戴良传》载:
及母卒,兄伯鸾居庐啜粥,非礼不行。良独食肉饮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毁容。或问良曰:“子之居丧,礼乎?”良曰:“然。”礼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礼之论?夫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实,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论者不能夺之。良才既高达,而论议尚奇,多骇流俗。
戴良和陈蕃、郭林宗是同时的人 ,年代尚在孔融之前,更有资格成为阮籍以下居丧不守礼的先驱者,所以葛洪追溯晋代傲放无礼的士风特别以戴、阮并举。 更值得注意的是《戴良传》中说他的哥哥居丧则“非礼不行”,这种一守礼、一违礼的尖锐对比,魏晋以下尤其成为风气。《世说新语·任诞》篇说: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
同书《德行》篇载: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注引《晋阳秋》,说和峤的“憔悴哀毁,不逮戎也”,意思是王戎比和峤更孝。如果阮、裴的故事表示自然与名教各得其所,那么王、和的故事则说明自然高于名教,也就是“情”比“礼”更重要。又据《典略》(《潜确居类书》卷七十引) ,“世谓伯鸾死孝,叔鸾生孝”,足证这种风气确与戴良有关系,虽然“生孝”、“死孝”的用法恰好颠倒了。我们无法判断这些个别故事的真实性, 但其中所显示的“情”与“礼”竞赛的风气是十分可信的。
崇尚自然的人既以“情”比“礼”更重要,父子之间的关系便不须注重“尊卑”之别,而当以上引《抱朴子》所谓“亲至”为主了。胡毋辅之和他的儿子谦之的关系最足以说明这种“亲至”的情形。《晋书》卷四十九本传说:
谦之字子光,才学不及父,而傲纵过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辅之亦不以介意,谈者以为狂。辅之正酣饮,谦之闚而厉声曰:“彦国(按:辅之字)年老,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辅之欢笑,呼入与共饮。
儿子直呼父字,照儒家礼法观念说,可谓忤逆之极。但父亲却不以为意,反而欢笑。这在近代西方社会不算稀奇,但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则真足骇人听闻。其实我们如果知道此时的人伦关系讲究的是“亲至”而不是“尊卑”,则这种情况也并无不可理解之处。《世说新语·伤逝》篇说: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问:“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注云“一说是王夷甫丧子,山简吊之” ,不论是王戎还是王衍,总之魏晋名士的父子关系已远越出儒家礼法之外。此外如王导和长子悦的关系 及郗愔临其子超之殡“一恸几绝”,都可以为王戎所说的“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作注释。推而及于兄弟,亦复如此。王子猷奔弟子敬丧,初都不哭,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 这是至性至情的流露,然而显然不合乎儒家的礼法。
夫妇之间的关系,魏晋时代也发生了基本的变化,亲密的情感代替了严峻的礼法。《世说新语·惑溺》篇言: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
荀粲是魏明帝太和时(227~232) 人,这是在夫妇关系上以情代礼的一个较早而著名的例证。《三国志》卷二十二《卫臻传》说:
夏侯惇为陈留太守,举臻计吏,命妇出宴,臻以为末世之俗,非礼之正。惇怒,执臻,既而赦之。
据《三国志·魏武帝纪》与《三国志·夏侯惇传》,惇领陈留太守在兴平元年(194年) ,而其时妇人参加宴会竟已成“末世之俗”,这也反映夫妇关系的变化。 到了葛洪的时代,这种风气则已发展得极其普遍。《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五《疾谬》说:
今俗妇女……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从诣之适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暐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道亵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反,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
不但妇女的社交游览的活动大为盛行,男女之间的交际也达到了相当不拘行迹的地步。葛洪继续告诉我们:
无赖之子,白醉耳热之后,结党合群,游不择类……携手连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观人妇女,指玷修短,评论美丑,不解此等,何为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隐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然落拓之子,无骨骾而好随俗者,以通此者为亲密,距此者为不恭,诚为当世不可不尔。于是要呼愦杂,入室视妻,促膝之狭坐,交杯觞于咫尺;弦歌淫冶之音曲,以誂文君之动心。载号载呶,谑戏丑亵。
葛洪是一个极端维护礼法的人,他的话自不免有故意丑化的地方。但他在这里所描绘的当时上层社会妇女生活的面影则大致可信。像“入室视妻”、“促膝狭坐”、“杯觞咫尺”种种现象在中国社会史上极为少见。葛洪屡用“亲至”或“亲密”来刻画当时的人际关系,尤其值得注意。正如父子关系一样,魏晋时期夫妇朋友之间的“亲密”也表现在称呼方面。《世说新语·惑溺》篇云: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晋书》卷五十《庾敳传》说:
王衍不与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为耳。”(按《世说新语·方正》篇,“耳”作“尔”)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
这两个故事,一属夫妇,一属朋友,但几乎如出一辙。“卿”字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是狎昵之称 ,足与《抱朴子》“亲密”之说互证。附带说明一句,这一时期有关妒妇的记载特别多,宋明帝至令虞通之撰《妒妇记》 ,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曾引及其书。妒风之盛显然和夫妇关系的亲密化有关,王戎之妇“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之问已透露其中消息矣。西晋时束皙撰《近游赋》 ,写他所向往的“逸民”生活,其中有云:
妇皆卿夫,子呼父字。
尤可证儒家的名教已不复为士大夫所重,无论是在父子或夫妇之间,亲密都已取代了礼法的地位。
(四)玄风南渡后的名教危机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到,汉末以来名教的崩溃不但是全面性的,而且这一危机表现在家族伦理方面较之在政治秩序方面更为深刻而持久。西晋统一以后,通过君主“无为”和门第“自为”的理论,大体上使政治方面自然与名教的冲突获得了满意的解决。但在家族伦理方面通过礼与情的特殊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名教与自然的冲突却发展到了表面化的阶段。据现存史料所见,破坏礼法的士风在西晋初年已很盛行,至元康(291~299) 时代更成燎原之势,此下一直到渡江之初,余势仍未衰。
……
但是这种风气并不限于少数“贵游子弟”,甚至朝廷大臣也都沾染上了,我们只需举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种情形。邓粲《晋纪》说:
王导与周顗及朝士诣尚书纪瞻观伎,瞻有爱妾,能为新声。顗于众中欲通其妾,露其丑秽,颜无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诏特原之。
这位周顗就是“风德雅重”、负海内重望、官至尚书左仆射的周伯仁,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 王敦谋逆时被杀。王导因当时没有救他,后来竟流涕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周顗至今还活在这句成语里。他的死倒表现得很有政治气节,自谓“备位大臣,朝廷衰败,宁可复草间求活,外投胡越邪!”临刑前痛骂王敦,“收人以戟伤其口,血流至踵,颜色不变,容止自若” 。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并不好用“轻薄无行”之类的考语加以一笔抹杀。只有通过当时极端破毁礼教的士风,周顗的行为才能得到确切的说明。否则以他这样一位众望所归的人物竟至当众欲通人之妾而露其丑秽,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渡江以后,南方关心伦理秩序的人,无论其思想为儒家或道家,都以纠矫任诞之风为当务之急。这一方面的史例很多,下面所选的是比较典型的。《晋书》卷七十《应詹传》载詹上疏元帝曰:
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同书同卷《卞壸传》:
阮孚每谓之曰:“卿恒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劳乎?”壸曰:“诸君以道德恢弘,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而谁!”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壸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然而闻者莫不折节。
应、卞两人,思想都倾向儒家,他们直以西晋之亡归罪于道家放达之风。王导、庾亮不从壸议,大概是因为此风太盛,一加推究则牵连必广。同书卷七十五《韩伯传》:
陈郡周勰为谢安主簿,居丧废礼,崇尚庄老,脱落名教。伯领中正,不通勰,议曰:拜下之敬,犹违众从礼。情理之极,不宜以多比为通。时人惮焉。识者谓伯可谓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与夫容己顺众者,岂得同时而共称哉!
史言简文帝居藩,引韩伯为谈客,则他自是玄风中人,但对于维护家族名教却不肯放松。看“识者”之议,更可以使我们了解当时破坏礼法的风气是多么地普遍。
高门放诞之士多逃难到了南方,因此北方的士风一般说来比较质朴、保守,但例外还是有的。
(五)情礼冲突——名教与自然之争的延续
从晋室南渡以后士风的放荡情形来看,名教的危机绝未因永嘉之乱而终止。所以广义的名教与自然的冲突无论在事实上或理论上都没有获得彻底的解决。这里有必要稍稍回顾一下魏晋以来名教与自然的争执。何晏、王弼调和儒道,虽然正式提出了名教与自然的问题,却并没有把两者放在对立的地位。嵇康、阮籍始公然以名教与自然互不相容,但是细察他们的言论,则他们所深恶痛绝的只是当时虚伪的名教,而不是理想的即合乎自然的名教。下至西晋时代,由王戎深赏阮瞻关于名教与自然“将毋同”的答语 ,以及郭象注庄与裴頠崇有等事例观之,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显然又已由矛盾而复归于统一。其中嵇康、阮籍的反名教,据陈寅恪先生的分析,则主要是由于他们(尤其是嵇康) 的政治立场与司马氏不同,不肯出仕。西晋以后,司马氏的政权既与高门世族的利益打成一片,东晋之初且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士大夫阶层已无所谓仕或不仕的问题。因此从政治观点说,名教与自然的冲突已失去其存在的依据了。
……
试看他在注中对《杨朱》篇“任情废礼”的思想如此热烈地赞扬,便可见礼与情的冲突在永嘉南渡数十年后仍然相当地严重。而范宁之所以特别把“中原倾覆”之罪归之于王弼、何晏,其着眼点也正是在“扇无检以为俗”的士风方面。名教危机的余波还在荡漾不已,并未过去。
如何解决实际生活中情与礼的冲突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在理论上肯定了情是一种社会价值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称情直往”能不能成为一种社会存在。前文已举出韩伯制裁周勰居丧废礼的例子,其他因破坏礼法而被中正降品或清议所废的故事还屡有所见。 可见关键不仅在于情而更在于礼,即怎样把礼变得合乎“礼意”。因此情礼冲突的真正解决不能单靠玄学家的清谈,更重要的,还要靠礼学家的革新。玄学和礼学的合流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唐长孺先生说东晋以后的学风是礼玄双修,玄学家往往深通礼制,而礼学专家则往往兼注三玄。 这是一个无可动摇的论断。不过礼玄双修之风并不完全是名教、自然合一说流行的结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它的兴起正是由于名教与自然合一之说还没有完成。名教与自然合一的全面完成有待于情与礼在实际生活中获得协调。因此我们必须把注意力从玄学转移到礼学。
(六)“缘情制礼”
我们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是礼学极端发达的时代,而南方尤其讲究丧服礼。清代学者沈垚曾指出六朝礼学是因维系门第而兴, 这一断案现已为史学家所普遍接受。1960年日本学者藤川正数出版了一部讨论魏晋丧服礼问题的专著,更使我们对于丧服礼和当时门第社会互相配合的情形获得了比较深入的认识。 藤川氏在“序说”中特别注意到魏晋丧服礼的一般历史背景及其与玄学思潮之间的关系。这正可说明东晋以下的礼玄合流不是单纯地出于谈辩名理的兴趣,而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门第社会中所存在的许多实际问题。
……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玄礼合流的实际意义,玄礼双方都在寻求具体问题的解决之道,而不是空谈自然与名教的合一。
通过礼制的革新以消弭情礼之间的冲突,使名教与自然合而为一,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在魏晋这一大变乱的时代中,尤其是晋室南渡以后,士大夫阶层在政治、社会以及家族秩序各方面遭遇到许多特殊而复杂的问题。维持秩序离不开礼制,而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又远非汉代以来的传统礼学所能应付得了的。在礼文不完备和条例的解释不统一的双重困难之下,礼学专家只有斟酌个别的情况随时制定新礼,或赋予旧礼以新的意义。因此“变通”成为这个时代礼学方法论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
儒家早有“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情与礼互为表里也不是什么新的观念,《荀子》的《礼论》篇和《礼记》的《礼运》篇中都可以找到这种说法,《史记·礼书》且明著“缘人情而制礼”之语,或即曹羲之所本。但是像魏晋以来的人这样处处把情礼紧密地扣在一起加以对举,则显然是一种新的态度。这不仅是一个名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魏晋时代的情与礼都取得了新的意义。
但是“缘情制礼”并不是完全放纵,容许在礼法上“任情不羁”。事实上这一时代的新礼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禁止居丧不守礼之类的情况,另一方面则是防止居丧过礼。魏晋以来因“哀毁过礼”以至“毁几灭性”的事例很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新礼法对过与不及都同样地加以限制,过礼有时候也是要受到批评甚至惩罚的。
(七)余论
总结地说,魏晋的名教危机持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其中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从汉末到西晋统一,这个危机主要暴露在政治秩序一方面。因此以士风而论,竹林七贤反抗性的放达最具有代表意义。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 这句话尤其能够说明这一阶段名教与自然冲突的政治性质(此层详见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书文选幽愤诗后》) 。到了西晋初年,司马氏的政权和势族高门打成一片,“君臣之节,徒致虚名” ,政治上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已失去其现实的根据。但是名教危机在一般社会秩序,特别是家族伦理一方面却全面地爆发了。阮瞻、王澄、胡毋辅之、谢鲲等人的“元康之放”便是第二代士风的典型代表。第二代对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已不发生兴趣,但他们继承并扩大了阮籍、王戎的任情废礼的精神,其结果是形成一种“妇皆卿夫,子呼父字”的风气,情与礼的冲突尖锐化而变成当时士大夫的生活与思想中的一个中心问题。郭象注庄,一则说“礼者,世之自行,而非我制”,再则说“知礼意者,称情而直往”,这是西晋初年情礼问题未获解决的确切表示。
永嘉乱后,名教危机随着玄风一起渡江,到了南方。关心社会秩序的人,无论是北人或是土著,儒家或是道家,在痛定思痛之余,都大声疾呼要消弭这一危机。但此时传统旧礼法既不足以适应已变的社会状态,而魏晋以来一直支配着士大夫生活的新的伦理价值——情——也不能完全置之不顾。因此如何革新旧礼法以安顿新价值,使情礼之间得到调和,可以说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东晋以后礼玄双修的学风便是在这种情势下发展起来的。从此以后,玄学世家多有兼治三礼之人,儒林传中也不乏善谈三玄之士了。《晋书》卷九十二《文苑·袁宏传》载宏作《三国名臣颂》,其中赞夏侯玄末语云:
君亲自然,匪由名教;爱敬既同,情礼兼到。
此语的前半截说名教出于自然不过是西晋以来的门面话,结尾“情礼兼到”四字才是东晋以下玄礼合流的真精神之所在。但是“情礼兼到”必须建筑在“缘情制礼”的坚固基础之上,这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功的了。
经过东晋以下一两百年的礼玄双修,再加上佛教的大力量,名教的危机终于被化解了。到了南朝后期士风已从绚烂而复归于平淡,虽则任情违礼之事偶然尚有所见。颜之推(531~590) 是南朝后期的人,而且由南入北, 他对江南的“士大夫风操”大体上是相当称许的。所以他说:
昔在江南,目能视而见之,耳能听而闻之,蓬生麻中,不劳翰墨。汝曹生于戎马之间,视听之所不晓,故聊记录以传示子孙。
《风操》篇所举避讳、丧礼、称呼诸项都是南方家族伦理的特色。从他所引“礼缘人情”一语便可见玄礼合流确有效验。清谈绝不完全等于空谈,即以清谈一事而论,不但谈士必须博学 ,而且清谈本身便发展出一套礼节,转为谈士的一种约束。《陈书》卷三十三《儒林·张讥传》:
后主尝幸钟山开善寺,召从臣坐于寺西南松林下,敕召讥竖义。时索麈尾未至,后主敕取松枝,手以属讥,曰:可代麈尾。
张讥没有麈尾便不能清谈,所以陈后主必须使人取松枝为代替品,可见用麈尾已成为清谈所不可少的“礼”了。东晋以后,大抵士大夫所共有的一些“情”,都有各种形式的“礼”起而与之相应。这是一个长期的“以礼化情”的发展过程。
名教危机下的魏晋士风是最近于个人主义的一种类型,这在中国社会史上是仅见的例外,其中所表现的“称情直往”,以亲密来突破传统伦理形式的精神,自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即士的个体自觉。这一点我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中已有比较详细的讨论。现在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名教危机在家族伦理方面持续之久及其解决之不易,我们就更不能相信魏晋的新士风只是少数人一时激于世变而发展出来的了。基本伦理价值的改变在整个魏晋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曾发生了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虽则这并不是唯一关键之所在。但是另一方面,魏晋正是士族开始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个别的士并不能离开家族基础而有其独立的社会意义。因此分析到最后,士的个体自由是以家族本位的群体纲纪为其最基本的保障的。这里我们看到了魏晋任诞之风的内在限制,“情礼兼到”是必然的归宿。尽管如此,因个体自由而激起的名教危机在中国社会史上还是留下了明显的痕迹。魏晋南北朝时代虽然南方和北方都是门第社会,但南北的家族组织则颇有不同。这一点,当时的人固然有切身之感,后世史家也每多论及。现在让我引两家之说于下,并参以史传,以为本文的结束。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北土重同姓”条:
世以同宗族者为骨肉。《南史·王懿传》云: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王懿闻王愉在江南贵盛,是太原人,乃远来归愉。愉接遇甚薄,因辞去(英时按:亦见《宋书》卷四十六《王懿传》)。又按,颜之推《家训》曰:凡宗亲世数,有从父,有从祖,有族祖。江南风俗,自兹已往,高秩者通呼为尊。同昭穆者,虽百里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梁武帝尝问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英时按:见《颜氏家训》卷二《风操》篇)予观南北朝风俗,大抵北胜于南。距今又数百年,其风俗犹尔也。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分居”条:
宋孝建(454~456)中,中军府录事参军周殷启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居,计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忌疾谗害,其间不可称数。宜明其禁,以易风俗。”(英时按:见《魏书》卷九十七《刘裕传》;原文见《宋书》卷八十二《周朗传》。“殷”乃“朗”字之讹)当日江左之风,便已如此。《魏书·裴植传》云: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赡诸弟,而各别资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隋卢思道聘陈,嘲南人诗曰:“共甑分炊饭,同铛各煮鱼。”(英时按:《隋书》卷五十七、《北史》卷三十本传均不载聘陈事。《太平广记》卷二四七诙谐三卢思道条有之,唯作“北齐卢思道聘陈”,诗首句“饭”作“水”,殆非顾氏所本,俟考)
吴曾指出北方重宗族,顾炎武则强调南方好分居,合起来看,正好显出南北门第的家族关系不同,即北方较亲而南方较疏。造成这种南北之异的历史条件当然很复杂,社会经济的因素尤其重要。 但是我愿意在这里别进一解,即南方宗族关系的疏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其源至永嘉乱后的玄风南渡。《梁书》卷二十八《夏侯亶传》云:
亶……辩给能专对。宗人夏侯溢为衡阳内史,辞日,亶侍御坐,高祖谓亶曰:“夏侯溢于卿疏近?”亶答:“是臣从弟。”高祖知溢于亶已疏,乃曰:“卿伧人,好不辨族从。”亶对曰:“臣闻服属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时以为能对。
这个故事显然就是上引颜之推《风操》篇之所本,足见当时流传甚广(按:颜氏转述于“族”下夺“从”字,易“服属”为“骨肉”,致不可解) 。夏侯亶用“服属易疏”四个字来解释北人“不辨族从”是否中肯是另一问题,但对于南方的宗族关系而言,这句话确是一针见血。而且夏侯亶既说“臣闻”,可见这个观念早已流行于南方,不是他临时编造出来的。“时以为能对”者,正是因为他能巧妙地利用一句南方现成的话来为北方人开脱也。玄风南渡把名教危机从中土移植到江南,为了消解危机,南方才有礼玄双修的学风,丧服的研究因此特别发达。服制讲究得越精微,宗族的亲疏关系也就分辨得越细致。因为唯有如此,普遍化的“礼”才能最大限度地照顾到个别化的“情”,使“情礼兼到”的境界成为可能。东晋以后“缘情制礼”的运动助长了南方士族的分居趋势,至少当时的人是这样地了解的。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序论
韦伯(Max Weber) 在今天西方的社会科学界和史学界中显然是处于中心的位置。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中有人向康德立异,也有人和他同调,但绝没有人能够完全不理会他的学说。 今天韦伯的情况便和康德十分相似。研究现代东亚社会和历史变迁的人则特别注重韦伯的《中国宗教》(The Religion of China) 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以下简称《新教伦理》) 两部著作。后一部书虽纯以西方的历史为对象,但其结论仍对东亚史的研究有反照的作用。韦伯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的解释涵蕴着一种理论的力量,可以从反面说明东亚——尤其是中国——何以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
但是近二三十年来,主要由于东亚地区(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 经济成长的特殊经验,不少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儒家伦理的积极功用。他们觉得韦伯对于儒家思想所持的否定看法也许有修正的必要。因此儒家——或者更广义地说,中国文化——是否曾对东亚的经济发展发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已引起海内外中国学术界的注意了。
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这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世界史学界所共同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从欧、美、日本到中国,我们都可以在历史论著和学报中找得到有关这一问题的大量的专题研究。但是对于这个共同关注的问题,史学界寻求答案的方式显然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流派:第一派从理论上断定资本主义必然会在中国史上出现,并且实际上已经萌芽,不过由于为种种特殊因素所阻,未能充分成长而已;第二派则并不预断资本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而是从事实出发,探讨传统中国为什么产生不出西方式的现代资本主义。第一派所持的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根据这个观点,历史五阶段论是适用于一切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中国当然不可能成为例外。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上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无数讨论都是这一历史观点的产物。第二派的史学家并不完全根据韦伯的理论,却都直接或间接地受了韦伯的一些影响。因此我们不妨说他们代表“韦伯式的”(Weberian) 观点。在西方和日本研究这个问题的史学家大致都可归之于这一派。
在更进一步地分析这两派的异同之前,我们有必要略略交代一下韦伯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新教伦理》这篇专论是否如柏森思(Talcott Parsons) 所说,乃为驳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作, 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在19世纪90年代的德国史学界,加尔文教派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本是一个讨论得非常热烈的题目,韦伯的研究正是闻风而起并有特殊突破的一个范例。 不仅如此,恩格斯在1892年为他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一书英文版所写的导论中,也明白地指出,加尔文的信条是适合新兴资产阶级需要的一种最大胆的主张。其“选民前定论”(predestination) 的意义便在于说明:在竞争的商业世界中,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往往不系于他的活动和聪明,而系于他所无法控制的外在情况。
这样看来,韦伯《新教伦理》一书似不能理解为专驳马克思主义的史观而作。但是往深一层看,这篇专题研究又确是和唯物史观针锋相对的。韦伯基本上是反对唯物史观的。就与本文有关的部分而言,我们可以举出以下几个论点:第一,韦伯不同意任何历史单因说,因此他也不能同意经济决定论。第二,他不取社会进化论,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正是社会进化论的一种最严格的表现方式。韦伯并不相信历史上有什么必然的发展阶段,当然更不能接受唯物史观的五阶段论了。第三,唯物史观基本上以上层的政治、文化结构是由下层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韦伯则坚持同样的下层基础可以有不同的上层建筑。不但如此,他显然认定文化因素——如思想——也可以推动经济形态的改变。这正是《新教伦理》一书的主旨所在。上引恩格斯关于加尔文信条的论断仍以“选民前定论”是资本主义竞争的一种“表现”(expression) ,这和韦伯以“前定论”有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之功是大有距离的。无论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怎样企图赋予思想以主动的功能,他们都绝不可能承认思想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可以达到如《新教伦理》所强调的程度。 从这一点说,《新教伦理》事实上确是对唯物史观的一种有力的反驳。
但是一旦把马克思或韦伯的观点应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上面,我们立刻便遭遇到一些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生的论断是完全根据西欧的历史经验而得来的。他的五阶段论也只是西欧社会经济史的一个总结。他把古代亚洲的社会经济形态含混地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正是要使它和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区别开来。总之,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说过,他的唯物史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1877年他在《答米开洛夫斯基书》(Reply to Mikhailovsky) 中特别强烈地反对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生的研究套用在俄国史上面。他毫不迟疑地指出,他的研究决不能变成一般性的“历史—哲学的理论”(historic-philosophic theory) ,更不能推广为每一个民族所必经的历史道路。他最后强调,在不同的社会中,即使表面上十分相似的事件,由于历史的处境相异,也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每一个社会的历史进化的形式都必须分别地加以研究,然后再互相比较,庶几可获得一种共同的理解线索。但是世界上绝没有某种一般性的“历史—哲学的理论”可以成为开启一切历史研究之门的“总键”(master key) 。因为任何“一般性的历史理论”都是以超越历史经验为其最主要的特色的。 马克思晚年之所以特别声明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是痛感于他的信徒把他的研究结果过度地推广了(甚至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在内) 。
如果我们尊重马克思本人的看法,那么今天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企图在中国史上寻找“资本主义萌芽”的种种努力便是完全没有理论根据的。马克思的历史著作为现代的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因而具有深刻的启示性,这已是史学界所久已公认的事实。但他似乎没有说过,中国传统社会必然会发展出西方式的现代资本主义。
据韦伯的说法,如果“资本主义”一词的意义是指私人获得的资本用之于交换经济中以谋取利润,那么不但西方古代和中古,甚至古代东方各国都早已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经济。 根据这个定义,当然中国从战国以来也已有“资本主义”了。这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商业资本主义”(commercial capitalism) 。但是西方近代工业革命以后所出现的资本主义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经验,是由许多个别历史因素的特殊组合而造成的。这样的资本主义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例子,而且也只能发生一次。关于这一点,我已在另一篇文字中有所说明,此处不再重复。
韦伯《新教伦理》的特殊贡献在于指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之外,还有一层文化的背景,此即所谓“新教伦理”,他也称之为“入世苦行”(inner-worldly asceticism) 。他认为加尔文派的“入世苦行”特别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兴起。所以他的《新教伦理》主要是以此派影响所及的区域为研究的对象,如荷兰、英国及北美的新英格兰等地。他特别征引了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的许多话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精神”。这一精神中包括了勤、俭、诚实、有信用等美德。但更重要的是人的一生必须不断地以钱生钱,而且人生便是以赚钱为目的,不过赚钱既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也不是为了满足任何其他世俗的愿望。换句话说,赚钱已成为人的“天职”或中国人所谓“义之所在”(calling) 。韦伯也形容这种特殊的精神是“超越而又绝对非理性的”(transcendental and absolutely irrational) 。但更奇妙的则是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之下,人必须用一切最理性的方法来实现这一“非理性的”目的。据韦伯的研究,加尔文的教义便是这一精神的来源。以新英格兰为例,由于这一精神的出现是先于资本主义的秩序的建立,因此它绝不如历史唯物论者所说,乃是经济情况的反映或上层建筑。相反地,它是资本主义的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韦伯《新教伦理》的主旨虽在阐明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兴起的文化背景,但他在此书中仍不忘其比较社会学和比较历史学的观点。所以,他认为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虽存在于中国、印度、巴比伦、西方古代和中古,但像上面所刻画的那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的精神”则起源于近代西方的新教地区。今天主张儒家伦理与现代东亚经济发展有关的学者因此便不免碰到一个理论上的困难:即使我们能证实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仍不足以推翻韦伯的原有理论,因为无论是日本、韩国或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其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而非发源于本土。
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研究与马克思派的唯物史观不同,它自始即不成其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理论,因此也就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套用在中国史上面。但韦伯的《新教伦理》一书却又和马克思本人的史学著作一样,其中含有新观点和新方法,足以启发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研究。首先,针对着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而言,韦伯认为思想意识也同样会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发生推动的作用。但是他又绝对不是一个“历史唯心论者”,认为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纯粹是宗教改革(Reformation) 的产物。他所要追寻的只是宗教观念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和扩展的全部过程中究竟曾起过何种作用。大体说来,他认定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归之于三个互相独立的历史因素,即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组织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思想。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必须在这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中求之,虽然《新教伦理》一书仅限于思想背景的分析。这一历史多因论的观点比唯物史观的单因论要复杂得多,其结论自然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得尽的。 此外,他的“入世苦行”说也蕴涵着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历史论点,即在一个社会从“出世的”性格转向“入世的”性格之际,其经济形态往往会发生重要的变化。这便是西方学人常常谈到的西方近代“俗世化”(secularization) 的问题。西方以外的社会(如中国) 也有在不同的程度上经过类似的历史阶段的,因此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带有普遍性的。但是由于程度上毕竟各有不同,因此史学家又不能用西方的经验机械地套用在其他社会的历史过程之上。例如加尔文教派的“前定论”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宗教怪论,我们绝不可能在其他文化中找到同样的东西。如果我们要运用韦伯的观点研究中国史,我们最多只能追问:在中国的宗教道德传统中有没有一种思想或观念,其作用与“前定论”有相当的地方然而又有根本的差异?这是韦伯观点的启示性之所在。所以分析到最后,我们只能提出一般性的“韦伯式的”问题,但无法亦步亦趋地按照韦伯的原有论著的实际内容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演变。因为一涉及实际内容,韦伯的个案研究便变得基本上和中国史不相干了。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马克思的史学理论(或任何其他西方学人的学说) 。我们不妨在中国史上提出“马克思式”(Marxian) 的问题,但同时也千万要记住马克思的名言,不要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本文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这一部分主要是研究中唐以来的新禅宗和宋以后的新道教。中篇,儒家伦理的新发展。这一部分着重讨论新儒家和新禅宗的关系,以及从程、朱到陆、王的发展。下篇,中国商人的精神。这一部分大致以16至18世纪为时代断限。但研究的重点不是商业发展的本身,而是商人和传统宗教伦理,特别是新儒家的关系。这三个部分虽是互相涵摄、彼此呼应的,但各篇也各有其独立性。
我们想追问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未进入中国之前,传统宗教伦理对于本土自发的商业活动究竟有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有影响,其具体的内容又是什么?读者当不难看出,我所提的正是所谓“韦伯式”的问题。但在试图解答问题时,我则尽量要求让中国史料自己说话。这样也许可以避免一种常见的毛病,即用某种西方的理论模式强套在中国史的身上。所以我的问题虽属于“韦伯式”,我的具体答案却和韦伯的《中国宗教》一书的论断大相径庭。
上篇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
宗教有它超越的一面,也有它涉世的一面。这便是传统宗教语言所说的“彼世”与“此世”之分。超越的彼世是否永恒不变、历久弥新,这恐怕永远是一个“见仁见智”而得不到最后答案的问题。但宗教终不能不与“此世”相交涉,而“此世”则不断地在流变之中。从宗教与“此世”之间的关涉着眼,我们当然可以讨论宗教的历史演进问题。
韦伯重视西方的宗教革命,特别是加尔文派的教义,因为他显然认定这是西方近代精神的开端。依照他关于“传统”和“近代”的两分法,中国与西方的分别即是前者仍属传统社会,而后者则已进入近代阶段。工业资本主义、科学和技术便是西方近代精神的最中心、最具体的表现,而这些恰恰是中国所缺少的。他在《中国宗教》一书中曾把儒家和清教派作了一番较为详细的对比。在这一对比之中,儒家和清教派几乎显得处处相反。 限于当时西方“汉学”的水平,韦伯关于儒家的论断在今天看来大部分都是成问题的。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他必须从宽发落。不过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在他的理解中,中国史从来没有经过一个相当于西方宗教革命的阶段。今天宗教社会学家的看法已有基本的改变。例如贝拉(Robert N.Bellah) 论近代早期的宗教(early modern religion) 便承认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儒学等都虽发生过类似西方新教那样的改革运动,不过比不上西方宗教改革那样彻底和持续发展而已。
……
大致说来,在南北朝至安史之乱之前,佛教在经济方面是靠信徒的施赐(包括庄田) 、工商业经营以及托钵行乞等方式来维持的。安史之乱以后,贵族富人的施舍势不能如前此之盛,佛教徒便不能不设法自食其力了。百丈怀海的清规和丛林制度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出来的。
……
我们从百丈和弟子的问答之间显然可看到这一教义上的革命在佛教徒的内心中确曾造成高度的紧张。因为以前佛教徒在事实上不能完全免于耕作是一回事,现在正式改变教义,肯定耕作的必要,则是另一回事了。推百丈答语之意,是说只要做事而不滞于事,则无罪可言。
……
我们虽然强调百丈怀海的禅宗革新对于新道教的兴起有深刻的影响,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否定新道教自有其内在的精神。这种精神也许可以看作是从晚唐到宋代的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不但见之于禅宗,也同样表现在新儒家和新道教的身上。新道教在方法上、组织上都可能受到禅宗的感染,然而精神则必须从内部发展出来,不能向禅宗借取。所以专从道教传统的本身来看,全真教是一个崭新的发展,至少当时的人是如此看待它的。
……
总结地说,新道教各派的兴起和发展充分地说明了一个重要事实:中国的宗教伦理自新禅宗以来即一直在朝着入世苦行的方向转变。新道教基本上是民间宗教,这一点在大多数道教史家之间已取得共同的认识。正因如此,这一新的宗教伦理才逐渐地随着新道教的扩展而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中去。南宋以来,《太上感应篇》之类的道教“善书”不断地出现并广泛地流行,这也是与新道教以俱来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大有助于新伦理在民间的传播。 新道教的宗教伦理在肯定此世,肯定日常人生方面比新禅宗更向前跨进了一步。禅宗已承认“鉏得一片畬,下得一箩种”是不虚过时光,已承认“砍柴担水,无非妙道”。但是他们还不能承认“事父事君”也是“妙道”。用现代的话说,他们还不能肯定社会组织的正面价值。新道教一方面沿袭了新禅宗所开始的入世苦行的方向,另一方面又受了儒学的影响。所以他们才更进一步地讲“事父事君”。真大道教“专以笃人伦、翊世教为本”和净明教以“忠孝”立教都是明证。这是新道教的“三教合一”。王重阳开宗明义,依据《孝经》、《道德经》和《般若心经》三部经典,尤其具有象征的意义。
新道教的伦理对中国民间信仰有深而广的影响。其中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思想便是天上的神仙往往要下凡历劫,在人间完成“事业”后才能“成正果”、“归仙位”(如《玉钏缘》弹词中的谢玉辉) 。同时凡人要想成仙也必须先在人间“做善事”、“立功行”。《太上感应篇》卷上说:“所谓善人……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即是这一思想的通俗化的表现。其实全真教的“打尘劳”,丘处机说“不遇境、不遇物,此心如何见得成坏”,便是神仙下凡历劫之说的一个远源。马钰教人“当于有为处用力立功立德,久久缘熟,自有透处”,丘处机教人“积功行,存无为而行有为”,这也与立善成仙的说法相去不远。这种思想正是要人重视人世的事业,使俗世的工作具有宗教的意义。人在世间尽其本分成为超越解脱的唯一保证。如果说这种思想和基督新教的“天职”(calling) 观念至少在社会功能上有相通之处,大概不算夸张吧!
中篇儒家伦理的新发展
儒家从来便是入世之教,因此并不发生所谓“入世转向”的问题。但是从韩愈、李翱到宋明理学,儒家确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是今天中外学人所共同承认的“新儒家”(New Confucianism) 。在上一篇论宗教的转向时,我们曾强调惠能以下新禅宗的历史意义。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在中国史上寻找一个相当于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的运动,则从新禅宗到新儒家的整个发展庶几近之。这一运动之所以从佛教发端则是因为佛教在唐代是中国思想和信仰的主流,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讨论的是:韩愈、李翱所首倡的新儒学和佛教的转向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其关系又属何种性质?
1.新儒家的兴起与禅宗的影响
合起来看,可知韩愈所倡导的正是后来宋明新儒家所谓“人伦日用”的儒学,与南北朝以来章句和门第礼学截然异趣。从这一点上说,韩愈的努力也未尝不表现着儒家的“入世转向”,也就是使儒学成为名副其实的“世教”。这一转向毫无疑问是受新禅宗的启示而来的。陈寅恪认为韩愈“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乃取法于新禅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 。这是一个很有根据的论断。
但是从韩愈以至宋代的新儒家明明都是全力排斥佛教的。现在我们却强调新儒家是继承了新禅宗的入世精神而发展出来的。这两种说法是不是有基本的矛盾呢?其实其中并无矛盾。新禅宗虽已承认“担水及砍柴”都是“神通与妙用”,甚至也承认“种种营生,无非善法”,但是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其否定“此世”、舍离“此世”的基本态度。他们对于儒家所最重视的“事父事君”的人伦世界仍不能正面地予以肯定。他们所能达到的极限是不去破坏“世教”而已。
2.“天理世界”的建立——新儒家的“彼世”
在韩愈的时代,只有新禅宗有心性功夫,儒家在这一方面是完全空白的。新禅宗对俗世士大夫的吸引力便在这里,因为“求心见性”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精神上的最后归宿之地,也就是所谓“安身立命”。朱子认为韩愈幸而未“向里”追索,否则也必然要被禅宗吸引过去了。朱子这样说也是有根据的,即韩愈在《与孟尚书书》中对大颠和尚所表现的倾服(《昌黎先生集》卷十八) 。由此可见新儒家想要从佛教手上夺回久已失去的精神阵地,除了发展一套自己的心性论之外,实别无其他的途径可走。宋明理学便是这样形成的。与韩愈同时的李翱则是为新儒家的心性论开先河的人。李翱有《复性书》三篇(见《李文公集》卷二) ,首先企图以《中庸》、《易传》为根据,建立儒家的心性学说。他的观点虽然没有完全摆脱佛教的影响,其开创的功绩则是不容否认的。 事实上,与韩愈相较,李翱的“入室操戈”对新禅宗具有更大的威胁性。正因如此,后世禅宗之徒才造出他最后终为药山惟俨所折服的故事。
李翱的《复性书》既是由入新禅宗之室而操其戈而来,则其论点不能完全脱尽佛教的纠缠自然是无足为异的。新儒家心性论要等到宋代才发展至成熟之境。但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新禅宗对新儒家的最大影响不在“此岸”而在“彼岸”。儒家自始即在“此岸”,是所谓“世教”,在这一方面自无待于佛教的启发。但是自南北朝以来,佛教徒以及一般士大夫几乎都认定儒家只有“此岸”而无“彼岸”。以宋儒习用的语言表示,即是有“用”而无“体”,有“事”而无“理”。这当然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智园(976~1022) 《闲居编》卷十九《中庸子传》说:
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蚩蚩生民,岂越于身心哉!嘻!儒乎?释乎?岂共为表里乎?世有限于域内者,故厚诬于吾教,谓弃之可也。世有滞于释氏者,往往以儒为戏。岂知夫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
智圆年辈在周、张、二程之前,其时新儒家尚未建立其心性论系统。所以他以修身、齐家、治国归之于儒,而独以“修心”属之佛教。这是“佛教为体,儒学为用”的两分论。从“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 唯一心”的观点说,儒家的世界其实是“虚妄”的,是由“一心”而造的。而唯一真实的“心”却落在佛教的手中。这便是宋代新儒家不得不努力建立自己的“彼岸”的基本原因。《程氏粹言》中有一段话云:
昨日之会,谈空寂者纷纷,吾有所不能。噫!此风既成,其何能救也!古者释氏盛时,尚只崇像设教,其害小尔。今之言者,乃及乎性命道德,谓佛为不可不学,使明智之士先受其惑。
新儒家因新禅宗的挑战而发展自己的“心性论”,这是最明白的证据。佛教内部对于“心”虽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以究竟义言,它还是归于空寂的,因为佛教的最后目的是舍“此岸”而登“彼岸”。新禅宗也不可能是例外。新儒家的“彼岸”因此绝不能同于佛教的“彼岸”,它只能是实有而不是空寂,否则将无从肯定“此岸”。朱子说:
儒释言性异处只是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
吾儒言虽虚而理则实;若释氏则一向归空寂了。
所以新儒家最后所建立的“彼岸”必然是一个“理”的世界或“形而上”的世界。程伊川对判划儒释的疆界曾提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说法。他说:
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圣人本天,释氏本心。
此处在“理”上添出一个“天”字即为保证此世界为客观实有而设。儒家不能采取佛教的立场,把客观世界完全看作由“无明所生”。程明道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这句话中的“天地万物”必须是实有的,不然此“仁者”将不必是“经世”的儒家,而可以是“出世”的禅师了。(禅宗和尚也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 所以宋明的新儒家无论其对“理”字持何种解释,都无法完全丢开“天”字。程朱一派认为“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十七《诸儒中之一》) 。这是“性即理”的立场,其中“天”是价值之源,分量之重,可不待论。主张“心即理”的陆王一派,虽极力把价值之源收归于“心”,但也不能真将“理”与“天”切断。象山、阳明都自觉上承孟子,但孟子的“四端”之“心”仍然是“天之所以与我者”。故阳明也常说“良知即天理”或“天理即良知”之类的话,不过此中“天”字的意义较空灵而已。
此处不能详论这两派在理论上的得失。 总之,这两派虽各有其内在的困难,但皆欲建立一超越的“理”的世界,以取代新禅宗之“道”,则并无二致。契嵩(1007~1072) 批评韩愈说:
韩子何其未知夫善有本而事有要也,规规滞迹,不究乎圣人之道奥耶?韩氏其说数端,大率推乎人伦天常与儒治世之法,而必欲破佛乘道教。嗟夫!韩子徒守人伦之近事,而不见乎人生之远理,岂暗内而循外欤?
这是新禅宗一方面的说法。照这一说法,儒家“守事”而“不见理”,“循外”而“暗内”。宋代新儒家的理论建构便以展示“人生之远理”为其中心任务,以破“佛教为体,儒学为用”之说,其具体结果之一则是上面所提到的“释氏本心,圣人本天”的判划。“天理”是超越而又实有的世界,它为儒家的“人伦近事”提供了一个形而上的保证。我们也可由此看出程、朱的“性即理”何以在宋代成为新儒家主流的一点消息。陆象山“心即理”的“心”虽也与禅宗的“心”有动静之别,实虚之分,但“宇宙便是吾心”之说 毕竟和释氏将万有收归一心的立场太相近。不但如此,“心即理”的提法又直接出于禅宗。契嵩《治心》篇云:
夫心即理也。物感乃纷;不治则汩理而役物。物胜理则其人殆哉!
可见象山“心即理”的观点很容易滑入禅宗的境界。王阳明的“致良知教”落到“心体”上也不免有此危险。其关键即在对客观世界的存在无所保证。这不是仅持一种“入世”的主观精神便能解决问题的。象山、阳明自然不是禅,但象山之后有杨慈湖,阳明之后又有王龙溪,则显然都流入禅。这是绝不能以偶然视之的。
新儒家因新禅宗的挑战而全面地发展了自己的“天理”世界;这是新儒家的“彼世”,与“此世”既相反而又相成。他们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来表示这两个世界:以宇宙论而言,是“理”与“气”;以存有论而言,是“形而上”与“形而下”;在人文界是“理”与“事”;在价值论领域内则是“天理”与“人欲”。此外当然还有别的说法,不必一一列举了。“此世”与“彼世”一对观念既相对而成立,则其中便必然不能无紧张(tension) 。不过由于中国文化是属于“内在超越”的一型,因此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不即不离的,其紧张也是内在的,在外面看不出剑拔弩张的样子。韦伯因为几乎完全没有接触到新儒家,在这一方面便发生了严重的误解。他认为所有宗教都持其必然而又应然之“理”(rational,ethical imperatives) 以对待“此世”,因而和“此世”的一切不合理之事形成一种紧张的状态。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是他却断定儒家对“此世”的事物,抱着一种“天真”的态度,与清教伦理,恰成一强烈的对照。后者将它与“此世”的紧张关系看得极其巨大而严重。相反地,儒家伦理至少在主观意向上是要将与“此世”的紧张减少到最低限度,因为儒家一方面相信“此世”即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世界,另一方面又相信性善论。总之,他认为儒家对“此世”的一切秩序与习俗都采取“适应”(adjustment) 的态度。
以我们今天的理解来说,韦伯所犯的并不是枝节的、事实的错误,而是有关全面判断的基本错误,但基本判断的错误仍然起于对历史事实缺乏充足的知识。儒家对“此世”绝非仅是“适应”,而主要是采取一种积极的改造的态度,其改造的根据即是他们所持的“道”或“理”。所以他们要使“此世”从“无道”变成“有道”,从不合“理”变成合“理”。关于这一点,下面将有讨论,暂且不多说。不过儒家的“此世”确是以“人间世”为其主要内容,对自然界则比较倾向于“适应”的一边。因此之故,“天理”与“人欲”之间的紧张在新儒家的伦理中才特别显得严重,无论程朱派或陆王派都是如此。程朱一派之所以提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分别,便是要通过对性善、性恶之争的消解以安顿“天理”与“人欲”的问题。其实“天命之性”即是孟子的“性善”,“气质之性”即是荀子的“性恶”。朱子说“孟子只论性,不论气”,“荀、杨虽是论性,其实只说得气” 可为明证。这二者的关系完全和“天理”与“人欲”一样,是永远在高度紧张之中,但又是不即不离的。朱子说:“人之为学都是要变化气禀,然极难变化。” 陈淳说得更明白:“虽下愚亦可变而为善,然工夫最难,非百倍其功者不能。” “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永不能分离,然而前者却又必须不断地去征服后者,则其间的紧张情况可以想见。这便是“天理”克制“人欲”的具体下手之处。朱子虽说过“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的话,我们却不能以词害意,认为他要消灭人的一切生命欲望。正当的生命欲望即是天理,这一点他交待得极其清楚:
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可见此处他是以过分的欲望称作人欲,有时他也称之为“私欲”。所以他用“人欲”一词有两重含义:一是正当的生命欲望,这是符合天理的,所以可以说“人欲中自有天理” ;另一含义则是不正常的或过分的生命欲望,这是和天理处于互相对立的地位的。“明天理、灭人欲”一语中的“人欲”便属于后一类。以第二含义的“人欲”(即“私欲”) 而言,则它是和“天理”永远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朱子说:
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便退也。譬如刘、项相拒于荥阳、成皋间,彼进得一步,则此退一步;此进一步,则彼退一步。初学者则要牢札定脚与它捱。捱得一毫去,则逐旋捱将去。此心莫退,终须有胜时。胜时甚气象!
《朱子语类》中此类描述甚多(参看卷五十九《孟子九·五谷种之美者章》) ,但以上引一条形容得最为淋漓尽致。朱子把天理和人欲(私欲) 的关系描写成一种长期的拉锯战争。试问新儒家的这种伦理会在“初学者”的心理上造成多么深刻的紧张状态?而且这种紧张也并不限于天理与人欲之间,它可以推广到理与气的一般关系上。《朱子语类》卷十二:
又问:若气如此,理不如此,则是理与气相离矣。曰:气虽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则理管他不得。如这理寓于气了,日用间运用都由这个气。只是气强理弱。……圣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这些子。
这个“理弱气强”的观点最能显出新儒家伦理与“此世”之间的紧张是何等巨大、何等严重。复由于理世界与气世界是不即不离的,无从截然分开,新儒家伦理又不容许人效道家的“逃世”,更不容许人为释氏的“出世”。这是一种“连体孪生”(Siamese twins) 式的紧张,自生至死无一刻的松弛。“圣人立教”则正是要人助“理”以制“气”。人能“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其根据即在此。但新儒家的“此世”毕竟偏重人间,因此朱子又说:
水之气如何似长江、大河,有许多洪流?金之气如何似一块铁恁地硬?形质也是重,被此生坏了后,理终是拗不转来。
朱子在这里便没有再说“圣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这些子”了。如果儒家的“圣人”也要“拗转”自然界“理弱气强”的局面,那就变成西方人“征服自然”的态度了。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的科学和技术,和新儒家的“理”的偏向是不无关系的。但是整体地看,上引韦伯的看法则显然是处处适得其反。新儒家是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此世”的负面力量的,时时有一种如临大敌的心情。通过对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发展,他们的新人性观事实上已综合了孟子的性善和荀子的性恶,而且其中恶的分量还远比善为重。他们绝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天真地相信人性自然是向善的。善出于“理”,恶来自“气”,但“理弱”而“气强”,这便需要修养功夫。从个人推到社会,其情形也是一样,政治和风俗都必须通过士的大集体不断的努力才能得到改善。儒家(尤其是新儒家) 对“此世”的基本态度从来不是消极地“适应”,而是积极地“改变”。在内在超越的文化型态之下,新儒家更把他们和“此世”之间的紧张提高到最大的限度。韦伯又说儒家认为“此世”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以新儒家而言,这也是完全不符事实的。《朱子语类》卷一:
问:“天地会坏否?”曰:“不会坏,只是相将人无道极了,便一齐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尽,又重新起。”
朱子在这里明明表示“此世”不必然是一个最好的世界。“此世”是好是坏完全系乎人。如果“人无道极了”,则这个世界也可以整个毁灭掉而重新出现一个新的世界。朱子这样说,正可见他对于“此世”是极为不满的。
3.“敬贯动静”——入世做事的精神修养
新儒家与新禅宗之间的关系具有微妙的多重性:一方面,新儒家乃闻新禅宗而起,但另一方面新儒家又批判并超越了新禅宗,而将入世精神推到了尽处。新儒家不但参照新禅宗的规模而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思想结构,并且在修养方法以至俗世伦理各方面也都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吸收了新禅宗的成分。
……
朱子说:
惟动时能顺理,则无事时能静;静时能存,则动时得力。……动静如船之在水,潮至则动,潮退则止;有事则动,无事则静。
表面上,“有事则动,无事则静”与新禅宗“动静二相,当体超然”甚为相似,但往深一层看,朱子以船与潮水为喻,即表明新儒家的“动”、“静”是同其方向。其“静时能存”的“理”是肯定“此世”并为“此世”的存在作最后保证的。新禅宗“心存道念”之“道”则是舍离“此世”的,其“动”、“静”显然分成两橛,背道而驰。所以新儒家必须更进一步把“理世界”与“事世界”之间的隔阂打通,这就落到了修养论层次的“敬”字头上,用朱子的话说,即所谓“敬贯动静” 。“涵养须用敬”本是程伊川立教的第一要目,但“敬”并不限于“存心养性”,以通向价值之源的超越境域,它也是成就此世之“事”的精神凭借。二程语录有一条说:
君子之遇事,无巨细,一于敬而已。简细故以自崇,非敬也;饰私智以为奇,非敬也。要之无敢慢而已。语曰:“居处恭,执事敬,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然则执事敬者,固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则“笃恭而天下平”矣。
由于“敬贯动静”,“敬”也必须成为入世做事的行动原则。朱子说:
二先生所论敬字,须该贯动静看方得。夫方其无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应物而酬酢不乱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俨若思”,又曰“事思敬”、“执事敬”。岂必以摄心坐禅而谓之敬哉!
朱子又在别处解释“敬”的含义说:
敬不是万事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
依此解释,则“敬”在入世活动中实为一种全神贯注的心理状态。后世中国社会上所强调“敬业”精神便由此而来。这是新儒家伦理中的“天职”观念,颇有可与加尔文教相比观之处,以下当随文附及。
如上篇所论,新禅宗和新道教的入世苦行都强调勤劳、不虚过时光、不作不食等美德。这些美德当然也随着“执事敬”的精神而出现于新儒家的伦理之中。克勤克俭、光阴可惜,这些都是儒家的古训,本无待外求,但是门第时代的儒家伦理对这一方面则重视不足。宋代以来的新儒家重弹古调不但有新的社会含义,而且也很可能受到了新禅宗入世运动的某些暗示。张载论“勤学”有云:
学须以三年为期。……至三年,事大纲惯熟。学者又须以自朝及昼至夜为三节,积累功夫。更有勤学,则于时又以为限。
他这里不是泛论“勤学”,而是具体指示学者要把一天分为三节,不间断地“积累功夫”。这似乎是取法于禅宗的“三时坐禅”(黄昏、早晨、晡时) 或“三时讽经”(朝课、日中、晚课) 。后来朱子屡说功夫须积累,不可间断,又说“早间”、“午间”、“晚间”都可分别“做工夫”(《朱子语类》卷八) ,这和张载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清代“理学名臣”曾国藩也把他的一天治事和读书的时间分为“上半日”、“下半日”和“夜间”三节。 新儒家对勤劳实具有更深刻的体认。与张载同时的苏颂(1020~1101) 说:
人生在勤,勤则不匮。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此其理也。
苏氏则更扩大了“勤”的范围,使它成为整个人生的基础。从“勤则不匮”一语来看,他所指的已不限于“勤学”,而包括士、农、工、商各阶层的人了。与“勤”相随而来的还有爱惜时光的意识。石介(1005~1045) 尝以爱日勉诸生曰:
白日如奔骥,少年不足恃。汲汲身未立,忽焉老将至。子诚念及此,则昼何暇乎食,夜何暇乎寐。
这种忙迫感在朱子教训门人时更是反复言之。例如他说:
光阴易过,一日减一日,一岁无一岁,只见老大。忽然死着,思量来这是甚则剧,恁地悠悠过了。
新儒家把浪费时间看成人生最大的罪过,和清教伦理毫无二致。在这一问题上新儒家其实也受到了佛教的刺激。所以朱子又说:
佛者曰:“十二时中除了着衣吃饭,是别用心。”夫子亦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须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闲用心,问闲事、说闲话的时节多。问紧要事,究竟自己事底时节少。若是真个做工夫底人,他是无闲工夫说闲话、问闲事。
朱子引佛家的话尚在引《论语》之前,则新儒家所受新禅宗的启发更无可疑。朱子不但反对“闲”,而且尤其反对“懒”。他说:
某平生不会懒,虽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懒不得。今人所以懒,未必是真个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才见一事,便料其难而不为。
朱子不但对门人如此说,对他的儿子也是一样。他在《与长子受之》(《朱文公文集·续集》卷八) 的家书中再三叮咛其子“不得怠慢”、“不得荒思废业”,必须“一味勤谨”,“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新儒家这种伦理对后世有莫大的影响。明初吴与弼“居乡躬耕食力,弟子从游者甚众”。有一次:
陈白沙自广来学,晨光才辨,先生手自簸谷,白沙未起。先生大声曰:“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又何从到孟子门下?”
新儒家的伦理是针对一切人而发的。通过“乡约”、“小学”、“劝农”、“义庄”、“族规”多方面的努力,他们想把这种伦理尽量推广到全社会去。明末清初朱用纯(伯庐) 的《治家格言》便是根据程朱伦理而写成的一篇通俗作品,在清代社会中流传极广。新儒家也有相当于“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伦理观念。范仲淹曾说:
吾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及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
朱子也说:
在世间吃了饭后,全不做些子事,无道理。
范、朱的“做事”自然不是指生产劳动。但儒家自孟子以来便强调社会分工,所以只需所做的是对全社会有益之事,而且取予相称,则接受奉养自无可愧。
4.“以天下为己任”——新儒家的入世苦行
宋代新儒家中范仲淹是最先标举这种“先觉”精神的人。朱子评论本朝人物,独以范仲淹“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并说: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
欧阳修撰《范公神道碑》也说:
公少有大节……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从宋代以来,大家一提起范仲淹几乎便会想到上引两条关于他的描述。“以天下为己任”是朱子对范仲淹的论断。 但这句话事实上也可以看作宋代新儒家对自己的社会功能所下的一种规范性的定义(normative definition) 。朱子用此语来描述范仲淹则是因为后者恰好合乎这一规范。“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是范仲淹自己的话,出于他的《岳阳楼记》。其中“当”字更显然是规范性的语词了。
……
新儒家起而与新禅宗相竞,自不能不争取社会上各阶层、各行业的人民,包括绝大多数不识字的人在内。所以早在宋代新儒学初兴时,张载已说:
凡经义不过取证明而已,故虽有不识字者,何害为善?
这种说法不但开陆象山一派的先河,而且明显地表示新儒家立教的对象是所有的人,不是某一特殊阶层。张载又说:
利之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犹言美之为美。利诚难言,不可一概而论。
这番话是答复学生的问题,可见他所关怀的对象不是“士”阶层而是所有的“民”。张载不但不许 “士”本身谋“利”,也不许国家(即政府) 与“民”争“利”。只有“利”于全“民”者才是正当的“利”。这是和他的“民吾同胞”的用意一贯的。新儒家内部虽有各种流派的分歧,但在“民吾同胞”这一个基调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新儒家伦理的普遍性不但表现在对“众生”一视同仁的态度上,而且也表现在重建社会秩序的全面要求上(用他们的名词说,即所谓“经世”) 。程、朱以《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其用意显然是首先确定革新世界的规模,因为《大学》从格致诚正一直推到修齐治平,对天下之事无一件放过。程、朱硬改“亲民”为“新民”,尤足以显示其建立新秩序的意向。朱子《集注》曰:
新者,革其旧之谓也。
这是新儒家全面“革新”的正式宣言,决不可等闲视之。陆象山和王阳明对《大学》的解释与程、朱大异,但无不接受这一基本纲领。 陆象山常说“道外无事,事外无道”(《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四) 又说“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卷二二) ,用意都一贯。……新儒家的“经世”在北宋表现为政治改革,南宋以后则日益转向教化,尤以创建书院和社会讲学为其最显著的特色。 由于这一转变,新儒家伦理才逐渐深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发挥其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这一关键上,我们必须略略交代一下程朱和陆王这两大宗派分化的意义。
5.朱陆异同——新儒家分化的社会意义
朱、陆思想的异趋不在本篇的讨论范围之内。上文已指出,新儒家各派的“经世”理想是一致的,他们都想在“此世”全面地建造一个儒家的文化秩序。同时,他们也同样都以“天民之先觉”自居,把“觉后觉”(包括士、农、工、商四民) 看作是当仁不让的神圣使命。但是在怎样去进行“觉后觉”的具体程序上,各家之间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以所谓朱陆异同而言,朱子可以说是专以“士”为施教的直接对象。他认为只有先使“士”阶层普遍觉醒,然后才能通过他们去教化其他的三“民”。他的“理欲之辨”、“义利之辨”首先便是对“士”所施的当头棒喝。在有机会的时候,譬如上封事和经筵讲义,他当然也不放弃向皇帝讲“正心诚意”。不过这种机会毕竟不多。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断定,朱子的直接听众是从“士”到大臣、皇帝的上层社会。他的文集和语录都可以为这一论断作证。他在《行宫使殿奏札二》说:
盖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
这是他的“读书穷理”的基本教法。这种话只能是对“士”和“士”以上的人而说的,对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便毫无意义了。陆象山则显与朱子不同,他同时针对“士”和一般民众而立教。不可否认地,象山的注意力主要还是集中在“士”的身上,但是他也常常直接向社会大众传教。以他的两次著名的公开演讲为例:第一次是淳熙八年(1181年) 应朱子之请在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专对“士”的训诫,其意在劝勉诸生“辨其志”,不要为科举利禄而读圣贤之书。 第二次是绍熙三年(1192年) 给吏民讲《洪范·五皇极》一章。这是群众大会上的讲话,除了官员、士人、吏卒之外,还有百姓五六百人。其主旨谓为善即是“自求多福”,不必祈求神佛。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主要哲学理论也在这次通俗演讲中透露了出来,即要人“复其本心”。他在讲词中特别指出:
若其心正、其事善,虽不曾识字亦自有读书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虽多读书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恶耳!
这是他信仰极坚的话,他从内心深处感到“士大夫儒者视农圃间人不能无愧”(《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四) 。
……
朱陆的分歧并不反映任何阶级利益的差异,但却和他们两人的家庭背景与社会经验的不同有关。朱子出身于士大夫的家庭,他的生活经验始终未出“士”的圈子之外。陆象山则“家素贫,无田业,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 。不但如此,据他的回忆,“吾家合族而食,每轮差子弟掌库三年,某适当其职,所学大进” 。可见陆家是商人出身,象山也富于管家的经验,直接和不识字的下层人民打过交道。如果他的回忆可信,那么他的学问并不是完全从书本上得来的。朱子和他的学生曾讨论到陆象山的社会背景:
问:吾辈之贫者,令不学子弟经营,莫不妨否?曰:止经营衣食亦无甚害。陆家亦作铺买卖。
宋代商业已相当发达,士商之间的界限有时已不能划分得太严格,因此新儒家也不得不有条件地承认“经营衣食”的合法性了。不过朱子在这条语录的后半段仍然多少流露了他对“以利存心”的戒惧心理。这本不足为异,清教徒的态度也是如此。从社会史的角度看,朱陆异同并不能在纯哲学的领域内求得完满的解答。早在南宋时代,新儒家的伦理已避不开商人问题的困扰了。
但南宋毕竟仍是士阶层居于领导位置的社会。陆象山一派在缺乏社会组织的支持的情形下,是不容易在民间大行其道的。程、朱一派专在士阶层中求发展,终于成为新儒家的正统。直到明代王阳明出现以后,陆、王才真正能和程、朱分庭抗礼,并且威胁到程、朱的正统地位。但这一新形势的造成也同样不能孤立地从思想史上得到完整的说明。最重要的是明代中叶以后四民关系上已发生了实质上的改变。关于这一点,我们将留在下篇中讨论。以下略述王阳明儒家伦理的新倾向以结束本篇。
王阳明的“致良知”教也是以“简易直接”为特色,但他的思想并不是直接从陆象山的系统中发展出来的。相反地,他的“良知”二字是和朱子“格物致知”的理论长期奋斗而获得的。朱子的“格物致知”本以读书为重点,是对于士阶层所立的教法。但天下的书是读不尽的,外在的事物更是格不尽的。若必待格物至一旦“豁然贯通”之境才能明理,才能做圣人,那么不但一般不识字的人将永远沉沦,绝大多数读书人恐怕也终生无望。所以王阳明二十一岁格竹子失败后便只好“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 了。但三十七岁时他在龙场顿悟还是起于“格物致知”四字。这时他“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致良知”之说当然可以在哲学上有种种深邃繁复的论证,但是从本篇的观点说,它的起源还是很简单的。王阳明仍然要继续新儒家未竟的“经世”大业。 他本人虽然和朱子一样,出身于士大夫的背景,但由于时代的影响,他必须同时以“四民”为立教的对象。因此他说:
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
又说:
我这里言格物,自童子以至圣人皆是此等工夫。但圣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费力。如此格物,虽卖柴人亦是做得。虽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良知教之所以能风靡天下正因为它一方面满足了士阶层谈“本体”、说“工夫”的学问上的要求,另一方面又适合了社会大众的精神需要。大体言之,王阳明死后,浙中和江右两派发展了前一方面,泰州学派则发展了后一方面。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1483~1541) 初为灶丁,后又从父经商于山东。以一个经商的人而能在儒学中别树一帜,这是前所未有的事(陆象山本人并未经商) 。泰州门下有樵夫、陶匠、田夫,尤足说明王阳明以来新儒家伦理确已深入民间,不再为士阶层所专有了。最值得注意的是陶匠韩贞,《明儒学案》卷三十三说他:
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毕,又之一村。
这种以农工商贾为基本听众的大规模布道是陆象山时代所不能想像的事。王学之所以能产生这样广大的社会影响,实不能不归功于王阳明的教法。“良知说”的“简易直接”使它极易接受通俗化和社会化的处理,因而打破了朱子“读书明理”之教在新儒家伦理和农工商贾之间所造成的隔阂。所以王艮能“指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学”。王阳明以来有“满街都是圣人”之说。此说解者纷纭,其实乃表示儒家入世承当的伦理非复士阶层所独有,而已普及于社会大众。法朗克(Sebastian Franck) 对宗教革命的精神曾有以下的概括语:“你以为你已逃出了修道院,但现在世上每一个人都是终身苦修的僧侣了。”这是说中古寺院中的出世清修已转化为俗世众生的入世苦行了。新禅宗的“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和王学的“满街圣人”都恰好是和此语东西互相交映。 清代焦循曾对“良知”学的社会含义提出一个看法。他说:
余谓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至若行其所当然,复穷其所以然,诵习乎经史之文,讲求乎性命之本,此惟一二读书之士能之,未可执颛愚顽梗者而强之也。良知者,良心之谓也。虽愚不肖、不能读书之人,有以感发之,无不动者。(《雕菰集》卷八《良知论》)
焦循文中的传统偏见可以不论,他所划分的朱子和阳明的界线也颇不恰当,但是他的确看出了一个问题:即朱子之学是专对“士”说教的,而阳明之学则提供了通俗化的一面,使新儒家伦理可以直接通向社会大众。这确是阳明学的历史意义之所在。新儒家之有阳明学,正如佛教之有新禅宗: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至新禅宗才真正找到了归宿;新儒家的伦理也因阳明学的出现才走完了它的社会化的历程。黄宗羲批评浙中的王畿“跻阳明而为禅”(《明儒学案》卷三十四) ,这些话都有充分的根据。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正是新儒家对新禅宗入室操戈的必然结果。新禅宗是佛教入世转向的最后一浪,因为它以简易的教理和苦行精神渗透至社会的底层。程朱理学虽然把士阶层从禅宗那边扳了过来,但并未能完全扭转儒家和社会下层脱节的情势。明代的王学则承担了这一未完成的任务,使民间信仰不再为佛道两家所完全操纵。只有在新儒家也深入民间之后,通俗文化中才会出现三教合一的运动。明乎此,则阳明后学之“近禅”便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传习录拾遗》第十四条云:
直问:“许鲁斋言学者以治生为首务。先生以为误人,何也?岂士之贫,可坐守不经营耶?”先生曰:“但言学者治生上,尽有工夫则可。若以治生为首务,使学者汲汲营利,断不可也。且天下首务,孰有急于讲学耶?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贰于治生?”
新儒家伦理在向社会下层渗透的过程中,首先碰到的便是商人阶层,因为16世纪已是商人非常活跃的时代了。“士”可不可以从事商业活动?这个问题,如前文所示,早在朱子时便已出现,但尚不十分迫切。到了明代,“治生”在士阶层中已成一个严重问题。有一则明人告诫子孙的“家规”说:
男子要以治生为急,农工商贾之间,务执一业。
明白了这一背景,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王阳明的学生竟一再向他提出这一点,并显然不满意他第一次所给的答案——“许鲁斋谓儒者以治生为先之说亦误人”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下篇还要继续有所讨论。更可注意的是:阳明第二次的答案比第一次要肯定得多,尽管他仍不能同意“治生为首务”。现在他竟说:“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我们无法想像朱子当年会说这样的话,把做买卖和圣贤等同起来。“心体无累”即“良知”作主之意。阳明教人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做买卖”既是百姓日用中之一事,它自然也是“良知”所当“致”的领域。阳明的说法是合乎他的“致良知”之教的。可见从朱子到阳明的三百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儒家伦理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些变化和发展便是下篇所要讨论的主题。
下篇中国商人的精神
宋代以来,商业的发展是中国史上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明清时代尤然。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近几十年来中外史学家已有大量的专题研究。本篇的讨论以商人的精神凭借和思想背景为主要对象,在时限上大致以16世纪至18世纪为断,也就是从王阳明到乾、嘉汉学这一段时期。至于商业发展的本身,此篇完全不拟涉及。
1.明清儒家的“治生”论
让我们先引清代沈(1798~1840) 关于宋代以来商人社会功能的变迁的一段观察,以为讨论的起点。沈在《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中说:
宋太祖乃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益甚。然而睦任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
这篇文字近人曾屡引之以说明宋元以后商人地位的变化 或科举制度的经济基础, 但由于它对于本篇的主旨特别具有重要性,所以值得予以更严肃的注意。首先必须指出,沈是一个乡试多次失败的寒士,他的话因此不免有激愤的成分。 不过整个地看,他的论点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上引的文字中包含了两个主要论点:一、宋以后的士多出于商人家庭,以致士与商的界线已不能清楚地划分。二、由于商业在中国社会上的比重日益增加,有才智的人便渐渐被商业界吸引了过去。又由于商人拥有财富,许多有关社会公益的事业也逐步从士大夫的手中转移到商人的身上。沈的用语略嫌过重,且统宋、元、明、清而言之,也失之笼统。但若把这一段文字看作是对16至18世纪中国社会的描写,则大致可以成立。他在此“序”的结尾处又再度强调:
元、明来,士之能致通显者大概藉资于祖、父,而立言者或略之。则祖、父治生之瘁,与为善之效皆不可得见。
可知沈对士的生活问题的关切确是发乎内心。这当然是和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分不开的。不但如此,他在“与许海樵”的几十封信中曾两度讨论到士的“治生”问题。其中一书云:
宋儒先生口不言利,而许鲁斋乃有治生之论。盖宋时可不言治生,元时不可不言治生,论不同而意同。所谓治生者,人己皆给之谓,非瘠人肥己之谓也。明人读书却不多费钱,今人读书断不能不多费钱。
在中篇论新儒家伦理时,我们看到士的问题早在朱子和王阳明的时代便已出现。阳明的弟子并且先后两次向老师问到许衡关于“治生” 的意见。现在沈又一再提及此说,可见这是明、清儒学中一重要公案。下面我将别引王阳明和沈之间的几位儒者的看法,以进一步讨论此一公案。这一讨论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了解王阳明以后儒家伦理的新动向,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说明士商关系的微妙变化。清初唐甄(1630~1704) 在《养重》一文中说:
苟非仕而得禄,及公卿敬礼而周之,其下耕贾而得之,则财无可求之道。求之,必为小人矣。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
唐甄宗主王阳明之学,但晚年转而经商。此文正是辩解他的“以贾为生”是为了保全自己人格的尊严。这一态度在明、清的儒家之中是有代表性的。全祖望(1705~1755) 《先仲父博士府君权厝志》云:
吾父尝述鲁斋之言,谓为学亦当治生。所云治生者,非孳孳为利之谓,盖量入为出之谓也。
钱大昕(1728~1804)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有“治生”一条,也引许鲁斋之说,予以肯定。他的结论说:
与其不治生产而乞不义之财,毋宁求田问舍而却非礼之馈。
由全、钱两人的口气来判断,他们似乎已无朱子、王阳明的顾虑,深恐一涉及“经营”或“治生”便于“道”或“学”有妨。相反地,他们好像很同情许衡以“治生”为“先务”的观点。如中篇所论,明代士大夫在家规中已强调“男子要以治生为急”,则清代更不难推见。关于这一点,还是沈讲得最透彻。他在《与许海樵》的另一封信中说:
衣食足而后责以礼节,先王之教也。先办一饿死地以立志,宋儒之教也。饿死二字如何可以责人?岂非宋儒之教高于先王而不本于人情乎?宋有祠禄可食,则有此过高之言。元无祠禄可食,则许鲁斋先生有治生为急之训。
又说:
若鲁斋治生之言则实儒者之急务,能躬耕者躬耕,不能躬耕则择一艺以为食力之计。宋儒复生于今,亦无以易斯言。
沈的话在清代儒家中有代表性。他所强调的是士必须在经济生活上首先获得独立自足的保证,然后才有可能维持个人的尊严和人格。但是最有意义的则是陈确(1604~1677) 在1656年(丙申) 所写的《学者以治生为本论》,这是正式讨论许衡“治生”说的一篇文献。陈确说:
学问之道,无他奇异,有国者守其国,有家者守其家,士守其身,如是而已。所谓身,非一身也。凡父母兄弟妻子之事,皆身以内事。仰事俯育,决不可责之他人,则勤俭治生洵是学人本事。……确尝以读书、治生为对,谓二者真学人之本事,而治生尤切于读书。……唯真志于学者,则必能读书,必能治生。天下岂有白丁圣贤、败子圣贤哉!岂有学为圣贤之人而父母妻子之弗能养,而待养于人者哉!鲁斋此言,专为学者而发,故知其言之无弊,而体其言者或不能无弊耳。
这篇文字之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是因为它正式针对着王阳明的观点——“许鲁斋儒者以治生为先之说亦误人”——提出了尖锐的反驳。照他的说法,儒者为学有二事,一是“治生”,二是“读书”,而“治生”比“读书”还要来得迫切。陈确所提出的原则正是:士必须先有独立的经济生活才能有独立的人格。而且他强调每一个士都必须把“仰事俯育”看作自己最低限度的人生义务,而不能“待养于人”。这确是宋明理学比较忽视的一个层次。因此陈确重视个人道德的物质基础,实可看作儒家伦理的一种最新的发展。在清代具有代表性的儒家之中,倾向于这种见解者颇不乏其人。
陈确是明遗民,他的话自然隐含有不仕异族的意味。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历史背景的特殊性,因而忽视这一新伦理观的普遍性。我们都知道陈确反对将“天理”和“人欲”予以绝对地对立化。他的“人欲正当处即天理” 和上引“治生”的说法基本上是同条共贯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戴震(1724~1777) 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所说的理欲关系,和陈确几乎如出一辙,这更不能视为偶然的巧合。 陈确虽然重视士的个人,却并未忘记士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他在《私说》中说:
或复于陈确子曰:子尝教我治私矣。无私实难。敢问君子亦有私乎?确曰:有私。有私何以为君子?曰:有私所以为君子。惟君子而后能有私,彼小人者恶能有私乎哉!……惟君子知爱其身也,惟君子知爱其身而爱之无不至也。曰:焉有(爱?)吾之身而不能齐家者乎!不能治国者乎!不能平天下者乎!君子欲以齐、治、平之道私诸其身,而必不能不以德之身而齐之治之平之也。
又曰:
彼古之所谓仁圣贤人者,皆从自私之一念,而能推而致之以造乎其极者也。而可曰君子必无私乎哉!
把《私说》和《学者以治生为本论》合起来读,我们便能认识到他对儒家思想的新贡献之所在。宋明的新儒家因为受到新禅宗的冲击,不免偏向于个人的心性修养。陈确的时代禅宗的威胁已不十分严重,因此他的重点便转移到个人的经济保障方面来了。总之,陈确相对肯定了人的个体之“私”,肯定了“欲”,也肯定了学者的“治生”,这多少反映了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一个新的变化。 从陈确、全祖望到戴震、钱大昕以至沈,儒家思想关于个人的社会存在的问题,似乎正在酝酿着一种具有近代性格的答案。一个儒家的人权观点已徘徊在突破传统的边缘上,大有呼之欲出之势了。
2.新四民论——士商关系的变化
由于明清儒者对“治生”、“人欲”、“私”都逐渐发生了不同的理解,他们对商人的态度因此也有所改变。而且16世纪以后的商业发展也逼使儒家不能不重新估价商人的社会地位。首先我们要引用王阳明在1525年(乙酉) 为商人方麟(节庵) 所写的一篇墓表,以见儒家在四民论上的微妙变化。王阳明《节庵方公墓表》略云:
苏之昆山有节庵方公麟者,始为士,业举子。已而弃去,从其妻家朱氏居。朱故业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从商乎?”翁笑曰:“子乌知士之不为商,而商之不为士乎?”……顾太史九和云:“吾尝见翁与其二子书,皆忠孝节义之言,出于流俗,类古之知道者。”阳明子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农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鹜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吾观方翁士商从事之喻,隐然有当于古四民之义,若有激而云然者,呜呼!斯义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闻欤?抑其天质之美而默然有契也。吾于是而重有感也。”
我们详引此表,因为它可以说是新儒家社会思想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此文的历史意义可以从几方面来说明。第一,方麟的活动时期当在15世纪下半叶。他弃去举业转而经商,这正是后世“弃儒就贾”的一个较早的典型。关于这一点,留待下文再说。第二,方麟早年是“士”出身,曾充分地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他在改行之后便自然把儒家的价值观带到“商”的阶层中去了。所以他给两个儿子写的信“皆忠孝节义之言,出于流俗,类古之知道者”。这便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说明儒家伦理是怎样和商人阶级发生联系的。这当然不是两者沟通的唯一渠道,但确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第三,同时也是最有意义的一点,即王阳明本人对儒家四民论所提出的新观点。这篇“墓表”是王阳明卒前三年所作,可以代表他的最后见解。本文中篇曾引及他第二次讨论“治生”问题,提出了“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之说。这条语录的时代虽不能定,但却与“墓表”的意见一致,可见阳明此篇绝非世俗的敷衍之作,而代表他的真正看法。他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虽然它以“托古”的姿态出现。大体上此文“托古”之意正与所谓“拔本塞源论” 相同,思路也相通,撰写的时间复相去不远。其最为新颖之处是在肯定士、农、工、商在“道”的面前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更不复有高下之分。“其尽心焉,一也”一语,即以他特殊的良知“心学”普遍地推广到士、农、工、商四“业”上面。他在同一年(1525年,乙酉) 所写的《重修山阴县学记》中说:
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阳明全书》卷七)
可见“尽心”两字的分量之重。商贾若“尽心”于其所“业”即同是为“圣人之学”,绝不会比士为低。这是“满街都是圣人”之说的理论根据。相反地,“墓表”中且明白地指出,当时的“士”好“利”尤过于商贾,不过异其“名”而已。因此,他要彻底打破世俗上“荣宦游而耻工贾”的虚伪的价值观念。王阳明以儒家宗师的身份对商人的社会价值给予这样明确的肯定,这真不能不说是新儒家伦理史上的一件大事了。
王阳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和沈“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其实说的是同一事,尽管字面上几乎完全相反。他们都是针对着士商之间的界线已渐趋模糊这一社会现象而立论的。所不同者,王阳明从儒家理想社会的观点出发而托于古,沈则以历史事实为根据而指出古今之异。阳明的新四民论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通过泰州学派王艮(1483~1541) 的社会讲学,这个理论已实际上传播到商贾农工的身上。王栋(1503~1581) 追述他的老师王艮的讲学功绩说:
自古农工商贾虽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学。……汉兴惟记诵古人遗经者起而为经师,更相授受。于是指此学独为经生文士之业,而千古圣人原与人人共明共成之学,遂泯没而不传矣。天生我先师(按:指王艮),崛起海滨,慨然独悟,直起孔、孟,直指人心,然后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灵,自完自足,不假闻见,不烦口耳。而二千年不传之消息,一朝复明。先师之功可谓天高地厚矣。
可证王艮所传的即是阳明的“四民异业而同道”之教。王栋所言纵略有夸张,但当不至与事实相去太远。岛田虔次研究泰州学派,以为与商业发达、庶民兴起有密切关系,并引此条语录代表中国近代精神的一个最高潮,这是很可以成立的历史断案。
另一方面,沈所说的“后世四民不分”也是明中叶以来受到广泛注意的一个社会现象。归有光(1507~1571) 《白庵程翁八十寿序》云:
新安程君少而客于吴,吴之士大夫皆喜与之游。……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程氏……子孙繁衍,散居海宁、黟、歙间,无虑数千家,并以读书为业。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
归有光的“士与农商常相混”与沈“四民不分”如出一口,但前者是16世纪的人,可见这一现象起源之早及持续之久。尤可注意者,此文在“士而商”、“商而士”之上都加上“所谓”两字,表示这两句话已是当时流行的成语。明代中叶以后,士与商之间已不易清楚地划界线了。程白庵是新安人,即属于著名的“新安商人”或“徽商”的集团。这一地区与儒家伦理的关系尤其密切,下文当再申论。事实上,明清作者所谓“四民不分”或“四民相混”,主要都是讲士与商的关系。明清社会结构的最大变化便发生在这两大阶层的升降分合上面。不但士人早已深刻地意识到这一变化,商人亦然。明人王献芝论及徽商时曾说:
士商异术而同志。
王献芝其人及年代未详,但此语与王阳明“四民异业而同道”几乎如出一口,更值得注意的则是李梦阳(1473~1529) 《明故王文显墓志铭》所引商人王现(文显) 自己的话:
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
王现(1469~1523) 和王阳明是同时代的人,他的“异术而同心”之说也与阳明的话若合符节。墓志铭的资料照例是由死者的家人提供的,所以我们并不能以此语归之撰者。李梦阳的祖父虽然出身商贾,他本人也与商人多所交往 ,但此铭中所引王现的话却和他的思想不合。他在《贾论》一文中 特别攻击“贾之术恶”,认为商人“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可见他对商人仍持有很深的传统偏见。我们既断定“士商异术而同心”确是商人自己的话,这条史料的价值便更值得重视了。他的训语后半段涉及商人的道德观念问题,留待后面再作进一步的分析。王现的话使我们看到明代商人也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已足以与士人相抗衡了。让我再引汪道昆(1525~1593) 的话以为旁证。汪道昆出身新安商人家庭,祖父以盐业起家,汪家又与新安名商吴氏、黄氏、程氏、方氏诸家有姻戚关系。所以他可以说是新安商人的一个有力的代言人。 他在《诰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程公暨赠宜人闵氏合葬墓志铭》中说:
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
“良贾何负闳儒”这样傲慢的话是以前的商人连想都不敢想的。这句话充分地流露出商和士相竞争的强烈心理。这一点下文将续有讨论。但我们若真正断定明代商人的心理确已发生了新的变化,便必须引前代商人的说法加以比较。这一方面的资料很难寻找,幸而欧阳修记录了一个北宋商人的议论,足以说明问题。欧阳修《湘潭县修药师院佛殿记》云:
湘潭县药师院新修佛殿者,县民李迁之所为也。迁之贾江湖,岁一贾,其入数千万。迁之谋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劳者,其得厚;用力偷者,其得薄。以其得之丰约,必视其用力之多少而必当。然后各食其力而无惭焉。士非我匹,若工农则吾等也。”
这位北宋大贾不但自觉不能与士比肩,而且以劳动价值而言,也有愧于农与工。因此他接着说:农与工“所食皆不过其劳。今我则不然。……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则过之。我有惭于彼焉。”这种说法才完全符合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把李迁之的话和王现的话对照着看,我们便不难发现从11世纪到15世纪,士与商之间的关系已起了相当基本的变化,而传统的四民观也已在实质上受到重要的修正了。
明清的儒家和商人都已重新估量了商人阶层的社会价值。这一重估事实上也是被新的社会现实所逼出来的。所以在明清文人的作品中,这一现实往往也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流露出来。姑举数例以证之。何心隐(1517~1579) 在《答作主》中说:
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
又说:
商贾之大,士之大,莫不见之,而圣贤之大则莫之见也。农工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商贾。商贾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士。商贾与士之大,莫不见也。使圣贤之大若商贾与士之莫不见也,奚容自主其主,而不舍其所凭以凭之耶?岂徒凭之,必实超而实为之,若农工之超而为商贾,若商贾之超而为士者矣。
这篇文字之特别有趣,是因他本不是讨论四民关系的,它的主旨是要人“主于圣贤”。但在无意之间,它竟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实况,即四民的排列是士、商、农、工。而且四民又可再归纳为两大类:士与商同属于“大”,而农与工则并列于社会的最低层。这是完全合乎实际的。18世纪的恽敬(1757~1817) 在《读货殖列传》中也说:
盖三代之后,仕者为循吏、酷吏、佞幸三途,其余心力异于人者,不归儒林,则归游侠,归货殖,天下盖尽于此矣。……是故货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大会也。
恽敬的话也是不自觉地反映了清代社会状况。他所讨论的其实只是士和商两类人,“游侠”不过是因为读《史记》而顺便提及而已。末句则透露了他对商人势力之大所发生的感慨。可见当时“心力异于常人者”不归之士即归之商。农与工当然不可能排在商之上了。不但士对商的估价如此,商人自己也是一样。李维桢(1547~1626) 《乡祭酒王公墓表》记陕西商人王来聘诫子孙之语曰:
四民之业,唯士为尊,然无成则不若农贾。
又韩邦奇《大明席君墓志铭》记山西商人席铭(1481~1523) “幼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
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于世,抑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
王来聘虽用“农贾”的现成名词,事实上他当然是说士而无成反不如商贾。席铭则十分坦率,明言得不到“功名”便从事商业,决不屑为农夫。可见根据商人的四民观,也是士为尊而商则紧随其后,农的社会地位则远在商之下。这和上引何心隐、恽敬的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
到了清代,我们甚至发现有士不如商的一种说法。归庄(1613~1673) 《传砚斋记》是为太湖洞庭山士商两栖的严舜工所作,其中有一段说:
士之子恒为士,商之子恒为商。严氏之先,则士商相杂,舜工又一人而兼之者也。然吾为舜工计,宜专力于商,而戒子孙勿为士。盖今之世,士之贱也,甚矣。
此处归庄引严氏先世“士商相杂”之例再度证实了他的曾祖父归有光“士商常相混”的观察。但是更可注意的则是他劝严舜工“专力于商,而戒子孙勿为士”之语。这句话当然不能从字面去理解。归庄是明遗民,他劝人经商而勿为士是出于政治动机,即防止汉人士大夫向清政权投降。明遗民的领袖人物中已偶有从事商业活动者,如顾炎武“垦田度地,累致千金” ,且相传与山西票号有关;又如吕留良因行医和从事刻书业,而被同辈攻击其“市廛污行” 。不过当时知名大儒从商者尚属例外,而不知名士人因政治原因而“弃儒就贾”者则为数或恐不少。兹举偶见之两三例如下。朱彝尊《布衣周君墓表》云:
君讳……幼治书,年十九丧父居忧,读丧祭礼,乡党以孝称。遭乱,乃弃举子业不治,就市廛卖米。
同文之末又记周故友之一云:
范路,字遵甫,自兰溪迁长水。经乱,卖药于市,有《灵兰馆集》。
姚鼐《鲍君墓志铭》云:
鲍氏世为歙人。明末有诸生遭革命不复出者,曰:登明……生子元颖,贾于吴致富。
这一类例子如果向文集、笔记、方志中去广为搜集,一定可以增加不少。 但以本篇主旨而言,以上诸例已经够说明归庄的弦外之音了。由此可知明清之际的政治变迁曾在一定的程度上加速了“弃儒就贾”的趋势。更重要的是这一变迁也大有助于消除传统四民论的偏见,使士不再毫无分别地对商人抱着鄙视的态度。
然而我们又不能过分强调政治的影响力。如果士之肯定商的社会价值完全出于一时的政治动机,那么我们便无法解释上述从王阳明到沈关于四民的新观念了。以下我们要选录明清几个商业繁盛地区的社会价值观来进一步说明这一论点。黄省曾(1490~1540) 《吴风录》说:
至今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
张瀚(1511~1593) 《商贾记》是16世纪中国商业世界的一个横剖面,极受近人重视。其中论福州会城及建宁、福宁地区云:
而时俗杂好事,多贾治生,不待危身取给。若岁时无丰,食饮被服不足自通,虽贵宦巨室,闾里耻之。
汪道昆《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云:
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赢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
又《荆园记》云:
休、歙右贾左儒,直以九章当六籍。
崇祯本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云:
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
雍正二年(1724年) 山西巡抚刘于义奏折云:
但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孙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
雍正朱批则曰:
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可笑。
以上所引资料或属16世纪或属18世纪,都与明清之际的政治变动无关。以地域而论,这些资料则概括了江苏、福建、安徽、山西各省。其中尤以徽州和山西两处最值得注意,因为这正是明清两大商人集团的产生地。这两地的人甚至把商业放在科举之上,这话虽可能有夸张,但至少使我们不能不承认传统的四民观确已开始动摇了。所以前引归庄的话除了政治含义之外,也还有涉及社会价值的深刻意义。无论如何,在传统四民观的支配之下,教子弟为商而不为士毕竟是很难想像的。这里我们要引宋代儒者的看法作为对照。陆游的家训(《太史公绪训》) 有一条说:
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教训童稚以给衣食,但书种不绝足矣。若能布衣草履,从事农圃,足迹不至城市,弥是佳事。……仕宦不可常,不仕则农,无可憾也。但切不可迫于食,为市井小人之事耳,戒之戒之。(叶盛《水东日记》卷十五“陆放翁家训”条)
放翁家训是叶盛(1420~1474) 从陆氏家谱中抄录出来的,不见于放翁集中,但其真实性则无可疑,因为其中所言与放翁思想完全吻合。放翁《东阳陈君义庄记》有云:
若推上世之心爱其子孙,欲使之衣食给足,婚嫁以时;欲使之为士,而不欲使之流为工商,降为皂隶。(《渭南文集》卷二一)
不难看出,陆放翁所根据的是典型的传统四民论。所以子弟只能在士、农二业中谋生,决不可流为市井小人。另一与放翁约略同时的袁采在《袁氏世范》中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说:
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仰事俯育之计,莫如为儒。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书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技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子弟之流荡,至于为乞丐、盗窃,此最辱先之甚。
袁采的标准比陆游的稍宽,但其坚持为士之意是很显然的。而且在万不得已必须改业时,商贾的位置也差不多排在最末。不过比乞丐、盗窃略高一二级而已。以陆、袁两家之说与明清时代某些地区“右贾而左儒”的倾向互较,中国四民观的新变化便十分清晰地显现出来了。我们不应过分夸张这种倾向,但历史事实是:从宋到明清,一般人对士与商的看法确已不同。明清的社会价值系统之所以发生了如此深刻而微妙的内在变化,其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本文无法详论。粗略言之,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是中国的人口从明初到19世纪中叶增加了好几倍,而举人、进士的名额却并未相应增加,因此考中功名的机会自然越来越小, “弃儒就商”的趋势一天天增长可以说是必然的。据重田德的研究,仅以安徽婺源一县而言,清代“弃儒就商”的实例便不下四五十个。 此外如明代山西也有大量的因举业不成或家贫不能继续读书而转入商业的例子。 第二,明清商人的成功对于士大夫也是一种极大的诱惑。明清的捐纳制度又为商人开启了入仕之路, 使他们至少也可以得到官品或功名,在地方上成为有势力的绅商。兹举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作为说明。洪亮吉(1746~1809) 《又书三友遗书》记汪中(1744~1794) 在扬州的故事,说:
岁甲午(1774年)余馆扬州榷署,以贫故,肄业书院中。一日薄晚,偕中至院门外,各骑一狻猊,谈徐东海所著《读礼通考》得失。忽见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舆访山长。甫下舆,适院中一肄业生趋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并曾至府中叩谒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颔之,不答也。
故事的后半段是汪中在愤极之余折辱了这位大商人。但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位扬州书院肄业生对商人的两次叩谒和见面时的礼敬。像汪中、洪亮吉这样的士人恐怕是少数,那个肄业生倒是有代表性。这岂不是18世纪士商关系一幅绝妙的白描图吗?不用说,商人的“三品章服”当然是捐纳得来的。
最后,关于新四民论出现的问题,我们还要澄清一个可能发生的疑问:即一般而言,元代的商人地位似乎在儒士之上,那么明清士商关系的变化是否直接渊源于蒙古人的统治?以我所知,元代恐怕只能算是特殊情形,对16世纪以后的社会变化至少看不出有直接的影响。蒙古政权所利用的巨商主要是所谓“色目人”,是《蒙鞑备录》中回鹘田姓(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曾考其人) ,如阿老瓦丁、乌马儿弟兄二人, 又如更著名的蒲寿庚,都是显例。 最重要的是儒家的社会价值根本未变,依然是“重农轻商”。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记姚枢(1203~1280) 向忽必烈献《救时之弊》三十条,其一即云:
布屯田以实边戍,通漕运以廪京都,倚债负则贾胡不得以子为母,如生牛,十年千头之法,破称贷之家。
所谓“以子为母”便是《黑鞑事略》中所说的蒙古统治者“皆付回回以银,或贷之民,而衍其息。一锭之本展转十年后,其息一千二十四锭”。这种高利盘剥在元代叫作“羊羔利”。姚枢是元初大儒,他在献策中力主重耕织、抑“工技”和“贾胡”,其用意正是要恢复传统的“四民”秩序。元代是儒士没有出路的时代,但是我们看不到16世纪以后那种“弃儒就贾”的现象,更看不到商人有“良贾何负闳儒”的自负。戴良在《玄逸处士夏君墓志铭》中记载了一位鄞县的成功商人夏荣达(1314~1361) 。但他是在“进退皆困”的情形下才“为货殖”的。他所崇敬的还是“士大夫”。《铭》曰:
君读书虽不多,然雅敬贤士夫而听其话言。子若孙必延名师儒以教。
戴良在《铭》末也说他“所就仅如此……惜乎才不为世用,志不行于时也”。夏荣达已是元末人,但士、商双方仍对商业的价值无所肯定。上面我们曾引了南宋陆游和袁采重“士”而轻“商”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元代也依然很强固。杨维祯(1296~1370) 《孝友先生秦公墓志铭》云:
余始来吴,闻昆、太仓为货居地。不为习屈,挺然以文行自立者,二人也。
这二人之一便是秦玉(1292~1344) 。《墓志铭》记他的话曰:
士读书将以惠天下,不幸不及仕,而教人为文行经术,亦惠耳。
这不正是陆、袁的话的再版吗?元代的盐商自然也显赫一时,但是很少有像汪道昆一类的作者来为他们唱赞词(参看程钜夫《雪楼集》卷十九《清州高氏先德之碑》) ,相反地,他们却遭到深刻的讥刺。杨维桢的《盐商行》有云:
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大农课盐折秋毫,凡民不敢争锥刀。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亭丁焦头烧海榷,盐商洗手筹运幄。大席一囊三百斤,漕津牛马千蹄角。司纲改法开新河,盐商添力莫谁何。大艘钲鼓顺流下,检制孰敢悬官铊。吁嗟海王不爱宝,夷吾之成伯道。如何后世严立法,只与盐商成富媪。
此诗显然认为元代法律对盐商过于宽大,而“盐商本是贱家子”之句尤其反映了传统“贱商”的观念。所以明代一开始,朱元璋便立刻回到汉代“法律贱商人”的旧格局中去了。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记:
(洪武)十四年(1381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
这些证据告诉我们:王阳明以来“四民异业而同道”之说绝不是直接从元代延续下来的。事实上,战国秦汉以降商人在中国社会上一直都很活跃。 但以价值系统而言,他们始终是四民之末。一直要到16世纪,我们才看到传统的价值观念有开始松动的迹象。虽然19世纪以后,传统的偏见依然继续存在,但是从王阳明到沈的许多见解在儒家社会思想史上则确是一个崭新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在明代以前找到商人活跃的事实,也不难在清代中叶以后仍发现轻商的言论,然而新四民论的出现及其历史意义则无论如何是无法抹杀的。
3.商人与儒学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讨论明清商人和儒学的一般关系了。
在未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必须先说明一点,即商人是士以下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个社会阶层。不但明清以来“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造成了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商业本身必须要求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商业经营的规模愈大则对知识水平的要求也愈高。即以一般的商人而言,明清时代便出现了大批的所谓“商业书”,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知识。据寺田隆信在日本《内阁文库》所见, 已有以下数种:
《一统路程图记》八卷 明黄汴撰 吴岫校 明隆庆四年序刊
《商程一览》二卷 明陶承庆 明刊
《士商要览》三卷 清憺漪子编 清刊
《路程要览》二卷 清刊
《天下路程》三卷 清陈其辑 乾隆六年刊
《示我周刊》全三卷附续集 清赖盛远 清刊
此外寺田氏又列举了以下两书:
《三台万用正宗》万历二十七年 余文台刊
《商贾便览》八卷 乾隆五十七年 吴中孚自序
谢国桢也介绍了三种:
《鼎镌十二方家参订万事不求人博考全编》明刊
《五刻徽郡释义经书士民便用通考杂字》残存二卷 崇祯刊
《新刻增订释义经书世事通考杂字》二卷外一卷 徽郡黄惟质订补 乾隆刊
最后一种即是第二书的增补本。 这些书可以说是商人为自己的实际需要而编写的,并且也是由商人刊行的。明、清商业书是从商人观点所编写的日用百科全书,从天文、地理、朝代、职官、全国通商所经的里程道路、风俗、语言、物产、公文书信、契约、商业算术以至商业伦理等无所不包。从这类书的大量出版和一再刊刻,我们可以看到商人必须对他们所生活的客观世界具有可靠的知识。书名中有“博考”、“通考”等字样更可能暗示着明清考证学兴起的社会背景。商人的世界观与终老一村的农民恰恰相反,也和不出户牖专讲心性的儒者不同;他们不能满足于主观的冥想,而必须了解广大的外在世界。以16世纪以来士商混而不分的情况而言,商业活动或竟是儒学向考证转变的一种外缘,也未可知,这一点不是本篇的主旨所在,姑不深论。
明、清又是小说、戏剧大为流行的时代。近人已多言其与城市商人阶层的兴起或有关系。15世纪的叶盛在《水东日记》中已指出:
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偶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读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读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有官者不以为禁,士大夫不以非;或者以为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助澜者,亦有之矣。
到了17世纪刘献廷甚至以小说、戏文比之六经,而说“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 。可见这种商人阶层所嗜好的民间文学愈来愈发达,也愈受士人的重视。冯梦龙(1574~1646) 、凌初(1580~1644) 所编的《三言》、《二拍》中往往取材于当时的商人生活,其中有些关于商人的故事,如《醒世恒言》中的《施润泽滩阙遇友》和《徐老仆义愤成家》或可在方志中证实其历史背景的真实性 ,或竟实有其人 。所以这些文学作品今天又成为我们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重要资料了。由于商业书和社会小说中都包含了通俗化的儒家道德思想,它们又构成了商人吸收儒家伦理的另一来源。此外还应该附带一提的则是民间宗教。黄宗羲《林三教传》曰:
近日程云章倡教吴、彰之间,以一、四篇言佛,二、三篇言道,参两篇言儒……修饰兆恩之余术,而抹杀兆恩,自出头地。余患惑于其说者不知所由起,为作林三教传。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程云章的三教运动。云章(亦作“云庄”) 名智,本是徽州典当商出身,落籍于吴,生于1602年,卒于1651年。他提倡三教合一必极有影响,所以同时代的黄宗羲才特别要写此传来揭破他的底细。这是17世纪徽商参加并领导三教运动的明证。 由此可见商人由于读书识字之故,直接吸收儒家及其他宗教伦理的机会是非常多的。程云章的例子更使我们了解:商人对于宗教和道德问题确有积极追寻的兴趣,不仅是被动地接受而已。
以儒家思想而言,商人早在16世纪已表现出主动求了解的愿望。何良俊(1506~1573) 《四友斋丛说》卷之四略云:
我朝薛文清(瑄,1389~1464)、吴康斋(与弼,1392~1469)、陈白沙(献章,1428~1500)诸人亦皆讲学,然亦只是同志。……何尝招集如许人?唯阳明先生从游者最众,然阳明之学自足耸动人。……而后世中才,动辄欲效之。呜呼!几何其不贻讥于当世哉!阳明同时如湛甘泉(若水,1466~1560)者,在南太学时讲学,其门生甚多。后为南宗伯(按:甘泉1533年升南京礼部尚书),扬州、仪真大盐商亦皆从学,甘泉呼为行窝中门生。此辈到处请托,至今南都人语及之,即以为谈柄。甘泉且然,而况下此者乎?宜乎今之谤议纷纷也。
何良俊是反对“讲学”的人,此书自序成于1569年,在张居正禁讲学前十年。因此他的议论未必完全公正。1533年以后扬州、仪真的大盐商向甘泉问学是出于其他的动机,还是对甘泉“到处体认天理”的说法发生了真正的兴趣,当然不易断定。但此时王阳明已死,他的弟子如王畿、王艮等正在轰轰烈烈地向社会各阶层展开传教运动。盐商中有人因此而产生了对理学的好奇心,也是很自然的事。根据上面关于士商关系的分析,我们应该承认甘泉的盐商弟子之中不乏求“道”之士。何良俊所说“到处请托”之事也许不虚,但是我们也不能据此而对盐商一笔抹杀。
商人之所以对儒学发生严肃的兴趣是由于他们相信儒家的道理可以帮助他们经商。16世纪的陆树声在《赠中大夫广东布政司右参政近松张公(士毅) 暨配陆太淑人合葬墓志铭》中说:
(士毅)舍儒就商,用儒意以通积著之理。不屑纤细,惟择人委任赀计出入。
这篇铭文中最触目的是“儒意”二字。但“儒意”在此究作何解?以上下文来看,张士毅并不指儒家的道德而言,毋宁指儒学中“治人”、“治事”以至“治国”的道理或知识。所以下文所强调的是“知人善任”的原则。换句话说,士人如何运用他们从儒家教育中所得来的知识以治理国家,商人便运用同样的知识来经营他们的商业。吴伟业(1609~1672)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例证。他在《卓海幢墓表》中介绍了一位浙江瑞安商人卓禺的事迹。其文略曰:
公讳禺,姓卓氏……居京师五载,屡试于锁院,辄不利,归而读书武康山中,益探究为性命之学。先是公弱冠便有得于姚江知行合一之旨。姚江重良知,颇近佛氏之顿教,而源流本殊。后之门人推演其义,以见吾道之大,于是儒释遂合。公既偕同志崇理学、谈仁义,而好从博山、雪峤诸耆宿请疑质滞。……公之为学,从本达用,多所通涉。诗词书法,无不精诣。即治生之术亦能尽其所长。精强有心计,课役僮隶,各得其宜。岁所入数倍,以高赀称里中。(《梅村家藏稿》卷五○)
卓禺显然也是一个“弃儒就贾”的人,《卓海幢墓表》不著其年代,但当略早于吴梅村。尤其难得的是:他的例子具体地说明了明清之际的商人中确有王阳明学派的信徒。他大概受到王畿一派的影响,因此有意汇合儒释。雪峤是雪峤圆信(1571~1647) ,浙江鄞县人。博山不易定为何人,疑是博山元来(1575~1630) 。另有博山智(1585~1637) 及博山道舟(1585~1655) 则嫌年代稍迟,不足与雪峤比肩。卓禺显然对理学和佛学都有很深的信仰,但他却凭借着这些精神资源以为经营商业之用。他可以说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一个典型例子。这可由他的从弟卓尔康(左车) 对他的评价获得实证。吴梅村引卓左车之言曰:
白圭之治生也,以为知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学吾术,终不告之。夫知、仁、勇、强,此儒者之事,而货殖用之,则以择人任时,强本力用,非深于学者不能辨也。今余之学不足以及余兄;而余兄之为善里中,尝斥千金修桥梁之圯坏者,岁饥出粟,所全活以百数。彼其于吾儒义利之辨,佛氏外命之说,深有所得,岂区区焉与废著鬻财者比耶!
白圭知、仁、勇、强之说出《史记·货殖列传》。这些虽然都是儒家的德目,但可以中立化(或普遍化) 而用之于货殖。这正可以说明上引张士毅所谓“用儒意以通积著之理”。这种“儒意”是广义的,不限于儒家的学说。从《货殖列传》和卓左车的话来看,其所指者毋宁是如何掌握商业世界的客观规律。因此卓左车所谓“非深于学者不能辨”,其“学”绝非儒家的“圣贤之学”,而是陶朱公、白圭之“学”,即以最理性的方法达到致富的目的。 但是卓左车后半段所说的“吾儒义利之辨”则是明指儒家道德观对卓禺的影响而言。其所举卓禺“为善里中”之事恰可证明沈所谓“睦任之风转见于商贾”。这类例子在明清文集中俯拾即是。总之,我们对吴梅村的《卓海幢墓表》细加分疏,便可知所谓“儒”与“贾”的关系必须分开两个不同的层次来理解。第一个层次的“儒学”指商人的一般知识和文化的修养,包括经、史、子、集各方面。由于这种修养必须通过儒家的教育才能取得,因此凡是受过教育的商人都可以说是具有“儒”的背景。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是一种广义的、知识性的“儒”。如前引陆树声所用的“儒意”便属此类。这种“儒”在道德上是中立的。第二个层次则是儒家的道德规范对于商人的实际行为所发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是有关商人伦理的来源问题。不过严格地说,这个问题也不简单,因为其中涉及个别商人的教育程度有高下之别。文化水准高的商人如卓禺,可以直接从王阳明的良知之教中汲取道德的启示,但是粗识文字的商人也许便要依赖通俗化的儒家伦理了。并且无论是高层文化或通俗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都已混合了释、道以及其他的成分。不但如此,中国的两层文化又无法清楚地划分界线。这些问题都给研究工作带来不易克服的困难。本篇但求观其大略,精密的分析在此是不必要的。
另一方面,我们把商与儒的关系分为两个层次乃是出于讨论上的方便,并不表示商人可以分成两类,有的专利用儒家的知识,有的专接受儒家的道德。事实上,就具体的例子而言,这两个层次也是往往混而难辨的。以下我们先讨论第二层次,即道德影响的问题。
上引卓禺是浙江人,因此早年便服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旨。这是商人受乡土儒风影响的显例。同样地,徽州商人也颇受朱子的感发。赵吉士(1628~1706) 说:
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掺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朱文公家礼,彬彬合度。
戴震(1724~1777) 在《戴节妇家传》中也指出:
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为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赵、戴皆休宁人,他们总结17、18世纪徽州的风气,当然是可信的。清代各地徽州会馆中“崇祀朱子”,而现存徽人族谱中也收入朱子的《家礼》。这些都是徽商尊崇朱子的明证。 徽商受朱子的影响,吴伟业的《汪处士传》提供了一个实例。徽州唐模村的汪凤龄(1583~1667) “试有司,辄不利”,他曾慨然叹息,曰:
吾新安非徽国文公父母之邦乎?今紫阳书院先圣之微言、诸儒之解诂具在,奈何而不悦学乎?且吾汪氏仕而显、贾而赢者,世有其人矣。苟富贵堙灭不称,何如吾为一卷师而以兔园终老也。
可见汪凤龄生于一个士商混而不分的家世,他的八个儿子后来都是“以孝谨起家,笃修行谊”的商人,他教训他们说:
陶朱公之传不云乎,年衰老而听子孙。吾心隐居废治生,诸子有志于四方甚善。但能礼义自将,不愧于儒术,吾愿足矣。
这个例子具体地说明了朱子的道德观念是怎样传播到商人身上的。
明、清商人对儒家思想抱有热烈的兴趣,还有其他的重要证据可资说明。首先是他们之中颇有偏好儒家的道德训诫如“语录”、“格言”之类。现在姑举几个例子如下:
(1)席本久(1599~1678) ,江苏太湖洞庭山的大商人之子。数不利于场屋,弃儒就贾。“暇则帘阁据几,手缮写诸大儒语录至数十卷。又尝训释《孝经》,而尤研精覃思于《易》。”
(2)席启图(1638~1680) ,是席本久的堂侄,亦洞庭山的大企业家。汪琬《席舍人墓志铭》曰:“君好读书,贮书累万卷。于是偏葺先贤嘉言懿行,条晰部居,共若干卷,名曰:畜德录。晚岁病风痹者数年,益键户著此书。尝题于书尾曰:‘吾病濒死,惟以书未成为恨。今幸少瘥,有不强力成书,而敢自惰偷者,没无以见先贤地下。’病不能转侧,至置书床箦上,俯睨之。盖其勤于问学如此。予故考君行事本末,以为得之先贤者居多。”(《尧峰文钞》同卷)
以上二例都出自洞庭山席家,叔侄之间可能互有影响。其中席启图不仅经营纺织业极具现代性 ,而且对宗族邻里的“睦任”也无所不至,又为沈的观察增添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所以汪琬说他的“行事得之先贤者居多”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3)章策(清代) ,徽州绩溪人,父卒后,弃儒就贾。他一方面“精管(仲) 、刘(晏) 术,所亿辄中,家以日裕”,但另一方面在经商时又勤阅“先儒语录,取其益于身心以自励,故其识量有大过人者。”(《西关章氏族谱》卷二六) 按:这个例子最便于说明上面所指出的儒商关系的两个层次。章策“精管、刘之术”,这是他受儒家教育(子、史之学) 所得到的客观知识。他因此而掌握了商业世界的规律,获致成功。但他同时又用“先儒语录”来律己,这便是他的商业伦理的来源了。
(4)王大来(1676~1712) ,籍贯不详。方苞记其兄王苍平之言曰:“昔吾兄弟三人,吾父命某学书,仲弟治家,而大来行贾。仲弟卒,内外事皆赖焉。凡可以适吾亲者,无不尽也。其家居戚党之窭艰者皆赖焉。父执某无子,奉以终其身。其客京师乡人,底滞而无归者,无不资也,而未尝有私财。……大来虽未涉书史,闻古今人懿行,必低回久之。入其闼,窗壁户牖皆所书格言也。其名虽不彰,实无愧士君子。其为我志之。”(《方望溪先生全集》卷十《王大来墓志铭》)
(5)佘兆鼎(1633~1705) ,安徽歙县人。方苞《佘君墓志铭》说他:“少废书,读《大学》未半。行贾后,益好书,日疏古人格言善事而躬行之。”(《方望溪先生全集》卷十一)
以上方苞所铭二人都是教育程度不高的中小商人。他们不研究“语录”,而专收集“格言”,这便说明他们的精神资源主要取自通俗文化中流传的儒家伦理。这一点是极可注意的。此外尚有几个例子,虽未标明“语录”、“格言”,而事实上也是同一类的。
(6)沈方宪,明末清初浙江海宁人。陈确《书潘烈妇碑文后》附记其事如下:“确十年前过硖山,访所亲,见纸屏上血书曰:‘愿终三年不饮酒,不食肉,不内寝。’问所亲:‘血书者何人也?’曰:‘余同居表兄沈方宪,为其父远客,死王事,旅榇未归故也。’‘何业?’‘业布米。’‘无论其志行,即其书,岂米贾哉!’曰:‘向固业儒,因贫无以为养,弃而业贾。’于是确胸中遂时时有一沈方宪。尝窃从硖之长老参察其日用,益知方宪不独志行笃实,能精勤慎密,以振起其家业。既为死父尽偿夙负,益以其余孝养母,勤抚教诸弟妹而婚嫁之,皆以礼。而硖人又亟称其贾法之廉平。确曰:‘异哉!今之儒者皆以学贾,而以方宪乃以贾学。若方宪者,真可谓好学矣。学岂惟举业之工已哉!’”(《陈确集》文集卷十七) 这又是“弃儒就贾”之一例。陈确说,沈方宪是“以贾学”,意即将儒家伦理推广到商业界,也就是王阳明所谓“异业而同道”。他以血书儒家丧礼之文于纸屏之上,更可见其信仰之诚而笃。他的“贾法廉平”必渊源于儒学伦理是无可置疑的。沈方宪的事迹在当时浙江曾传为美谈,所以张履祥(1611~1674) 的《言行见闻录》也记其事曰:
海宁沈方宪,本旧族,贸易硖石市,皆服其不欺。性笃孝,父母没,刺血书“不饮酒,不吃腥,不内寝”九字于起居之所,守之不变。其妹适里中潘氏,夫死,毕殓事,恸哭七日而卒,人称其殉节。(陈确文末原注所引)
张氏所记除“父母没”当作“父没”之外,和陈确所亲见者完全一致。这应该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绝非谀墓文溢美之词。但因有沈方宪血书纸屏之事,上举“语录”、“格言”的可信性也更为增加了。
(7)周世道(1722~1786) ,杭州盐商。卢文在1786年撰《周君坦之家传》曰:“君少英敏好学,年十七因金门公以劳得疾,所遗业几折阅,又无可委托者,不得已以身肩之。节啬诸无名费,于后始稍稍复振。弟敬之殁时,孤载章始周岁。君抚爱教笃甚至,年十九,举于乡。他若营先人窀穸,修祠宇、家乘等事,罔不竭力,以为诸子姓兄弟倡。其训子则曰:‘居家以孝友为本,处世以和平为先。’呜呼!君实允蹈斯言。忆余弱冠时,尝得君家乘读之,大率皆以孝友著。今君可无愧其先人矣。”周世道是卢文的表弟,故后者对他的家世知之甚详。这是一个盐商世家,但其所遵行的则是典型的儒家伦理。卢文在传末论曰:“吾闻君临财也廉,故能不失其孝友之绪。” 他在此以“廉”为“孝友”的引申,是和沈方宪的例证相符合的。
卢文所引周世道训子之语即是当时所谓“格言”。清代《士商要览》有一则特别强调“凡人存心处世,务在中和” ,即与“处世以和平为先”的意思完全相同。可见这是当时商人信条之一。
(8)瞿连璧(1716~1786) ,浙江嘉定人。钱大昕(1728~1804) 《瞿封翁墓志铭》云:“翁九岁而孤,哀毁已如成人。后以家计中落,治生为急。吾乡地产木棉,衣被四方,乃于吴门经理贸迁。试计然之术,积其奇羡,遂至饶裕。翁性耿介,动必以义,不苟然诺。虑事精审,纤悉毕周。治家接物,皆中法度。……手定宗谱,条例井井。故居在儒学之南,岁久敝漏。翁既葺而新之,后虽徙家吴阊,犹以学南自号,示不忘本也。少从侍御时西岩先生受业,故熟于邑中旧事,谭论乡先辈嘉言善行,不倦。其训子孙,严而有法。……晚岁多储方药,服食惟谨。尝举古人‘善言不离口,善药不离手’之语,为予诵之。”
瞿连璧的祖父曾以“明经起家”,即中过举人,而他的次子和好几个孙子也都“习儒”,其中之一便是钱大昕的女婿。这又证实了沈“四民不分”及“士多出于商”的论断。瞿连璧好谈“乡先辈嘉言善行”,即是平时留意“语录”、“格言”之类。他所引“古人之语”是唐代孟诜的话,原文是“养性者善言不可离口,善药不可离手” 。但瞿连璧受教育程度不高,未必读过《新唐书》。“古人之语”当是钱大昕知其语源而加上去的。其实此语在清代早已成为民间流行的谚语了。翟灏《通俗编》成于18世纪上半叶(有周天度乾隆十六年,即1751年《序》) 。其书卷十七《言笑》类已收入此条,可证瞿连璧之能够信口道出,正是因为他一向留心搜集“格言”的缘故。
以上所举商人重视“语录”、“格言”八例,在时间上涵盖了17、18世纪,以地理言则分布在江苏、安徽、浙江三省,都是商业特别发达之区。必须说明,我并未有心寻找这类记载,以上所引的只不过是在阅读诸家文集的过程中偶然摘录下来的几条罢了。如果刻意去做系统的搜集,所得当远不止此。但是我深信这些抽样而得来的例子是有相当代表性的,至少已足以说明本篇的主要论点之一。明清商人究竟关不关心道德问题呢?他们是否曾主动地去建立自己的道德规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们的道德源头何在?又是通过何种具体的方式而得来的?这些都是相当吃紧的问题,而且不能以“想当然耳”的办法作模糊笼统的解答。我相信以上八例已对这些问题提供了部分的答案。由于这些实证的支持,我们对于前面所引16世纪时扬州大盐商向湛若水问学的记载也必须重新估定其意义了。以下我们将检讨商人的道德实践的问题。
4.商人的伦理
明清商人伦理是一个极有趣而又复杂的问题,限于篇幅,本节只能从其典型意义上作一概括性的讨论。我们的重点是在说明商人在伦理上的实践,不仅是他们持有某些道德信条而已。但是这里我们碰到一个方法论上的困难:我们固然可以找到不少明清商人实践其道德信条的证据,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实践究竟有多少代表性?据我对于有关的这一方面的明清史料的认识,这个问题是无从用量化的方法求得解决的。不过这一方法论上的困难在史学上是普遍性的,它同样存在于韦伯有关新教伦理的研究之中。我们只能说:这个问题和史学家对于他们所研究的历史世界的全面判断有关。如果我们承认明清的商业世界中存在某种秩序,而此秩序又多少是由某些伦理观念在维系着,那么当时文献中所透露的占有主导性质的商人伦理便应该受到研究者的严肃注意。至少到今天为止,言行完全一致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还没有存在过。而言行完全相反或基本上背道而驰则是社会秩序即将或正在崩溃的象征。以16至18世纪的中国社会而言,商人阶层正处在上升发展的阶段,因此当时流行的商业道德对他们大体上确是发挥了约束的作用的。明清商人中虽有欺诈之事,如明末《杜骗新书》之所示,却不足以否定商业伦理的存在。16、17世纪的欧洲和英国商人又岂能人人都依新教伦理而行,全无欺诈之事?即以今天的情形而言,我们也不能因为有经济犯罪的现象而否认经济世界中仍受某种伦理规范的支配。事实上,“欺骗”或“犯罪”正是相对于某种公认的“规范”才能成立的概念。因此以下仅在客观地刻画出一般的常态,绝不是美化传统的商人,说他们人人都遵守商业道德。特声明于此,以免读者误会。
韦伯论新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首推“勤”(industry) 与“俭”(frugality) 两大要目。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勤俭则是最古老的训诫。“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早见伪古文《尚书·大禹谟》,其源甚古。李商隐《读史》诗也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但是必须指出,“勤俭”的信条因宗教的入世转向而更深入到日常人生之中。无疑地,禅宗的“不作不食”,新道教的“打尘劳”和新儒家的“人生在勤”及“懒不得”都更加深了中国人对勤俭的信仰。到了明清时代,这种勤俭的习惯便突出地表现在商人的身上。山西和徽州两大商人集团的一般作风最能够说明这一问题。谢肇(1567~1624) 《五杂俎》说: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然新安人衣食亦甚菲啬,薄靡盐薤,欣然一饱矣,惟娶妾、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
初看这条记载,好像是山西商人“俭”,而徽州商人“奢”。但再读下去,谢再杭又承认新安商人也是自奉甚薄,并非一味奢侈。我们在其他记载中当然也可以见到“新安奢”的说法。例如汪道昆《汪长君论最序》说:
新安多大贾,其居盐者最豪,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召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坐尽欢,夜以继日。
这条资料出自新安人之手,大足坐实《五杂俎》之说。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其中尚有复杂的背景。以明代扬州的盐业而言,山西商人和政府的关系较好,因此远比新安商人占优势。例如嘉庆《两淮盐法志》说:
明万历中定商灶籍,两淮不立运学,附入扬州府学。故盐务无册籍可稽。且有西商,无徽商,亦偏而不全。
商、灶两籍是专为盐商子弟在科举中所保留的应试特权,使他们可在本籍之外经商地区报考生员。明代扬州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这便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的明证。 甚至在清代早期,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优势也依然没有动摇。 徽商为了争取上风,自不能不采取交际的方式以笼络政府官员。上引谢、汪两家关于新安大贾“奢”的记述似乎都集中在搞好“公共关系”的一面,这是很可注意的。“娶妾”、“宿妓”正是“召客高会”的场合。李梦阳任户部郎中时撰“拟处置盐法事宜状”,其中论及扬州盐商有云:“今商贾之家……畜声乐伎妾珍物,援结诸豪贵,藉其荫庇。”(《空同先生集》卷三九) 尤可为明证。至于“争讼”则更是为了在法律上争取自己权利,不能算作“奢” 。顾炎武《肇域志》说:
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青衿士在家闲,走长途而赴京试,则短褐至,芒鞋跣足,以一伞自携,而吝舆马之费。闻之则皆千万金家也。徽州人四民咸朴茂,其起家以资雄闾里,非数十百万不称富也,有自来矣。
可见一般而言徽商仍然是以“勤俭”为其基本特色的。
在明清商人伦理中“诚信”、“不欺”也是占有中心位置的德目。韦伯在《中国宗教》一书中特别强调中国商人的不诚实(dishonest) 和彼此之间毫不信任(distrust) 。他认为这和清教徒的诚实和互信形成了尖锐的对照。但他又对和外国人做生意的中国行商(Ko Hang,即Cohong) 的信誉卓著大惑不解,以为或是因为行商垄断对外贸易,地位稳固之所致。他并且进一步推论,如果行商的诚实是真的,那一定也是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不是从内部发展出来的。 韦伯的说法大有商榷的余地。是否19、20世纪中国商人的伦理已大不如前,这一点尚有待于经验研究的证实或否证。但以16至18世纪的情形而言,中日研究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肯定了中国商人的诚信不欺。研究者已举出了无数具体的例证,限于篇幅,这里一概不加引证了。 韦伯不能直接利用中文资料,所以这一层可不深究。最不可解者是他在《新教伦理》中明明强调清教徒有一种特殊的”上帝“观,即人除了完全信任”上帝“外,对任何人(包括最亲密的朋友) 都绝对不能信任。 他在两部著作中竟对清教徒的伦理观作了完全相反的解释,这便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了。
韦伯对中国商人的误解起于他看错了中国的价值系统。他认为中国人缺乏一个内在的价值核心(absence of an inward core) ,也没有某种“中心而自主的价值立场”(central and autonomous value position) 。换句话说,即没有超越的宗教道德的信仰。现在姑就这一点举例说明。“诚”与“不欺”是一事的两面,在新儒家伦理中尤其占有最中心的位置。在理学大兴之前,这两条德目已成为儒家道德的始点。范仲淹以为“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 。刘器之追随司马光五年,只得到一个字:诚。司马光向他解释:“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这当然是他精研《中庸》之所得。而致“诚”之道则必须自“不妄语人”即“不欺”始。经过长久的修养,一个人最后才能达到“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有余地”的境界(见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 。“诚”和“不欺”上通“天之道”,这便为此世的道德找到了宗教性的超越根据。经过新儒家和民间宗教的长期宣说,这种观念在明清时代已深深地印刻在商人的心中。康海(1475~1541) 在《扶风耆宾樊翁墓志铭》中记商人樊现(1453~1535) 语:
谁谓天道难信哉!吾南至江淮,北尽边塞,寇弱之患独不一与者,天监吾不欺尔!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谁谓天道难信哉!
可见这位陕西商人对“天道不欺”的观念信之甚笃。在本篇第二节,我们已引了李梦阳《故王文献墓志铭》记山西王现“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等语。让我们再引《扶风耆宾樊翁墓志铭》中所载他父亲的一段话。王现以信义待人,有一次逃过了盗劫,他的父亲闻之,大惊喜,曰:
现也,利而义者耶!然天固鉴之耶!
王现的父亲是一贫士,曾任教谕,他对“天”的信仰大约来自儒家。王现本人也是“弃士而就商”(《扶风耆宾樊翁墓志铭》语) 的,足证他的“天之鉴”之渊源所在。明清商人不但信“天”,而且也信“理”。民国初年修《婺源县志》记载一位晚清商人潘鸣铎云:
性孝友,幼读四子书,恒以不尽得解为憾。静思数日,谓圣学不外一理字,豁然贯通,非关道学之书不阅。……方某运茶,不得售,欲投申江自尽。铎照市价囤其茶,遣归。后寄番售,余息银五万两,仍与方某。
这个例子正在19世纪下半叶,新儒家“理”的观念仍深入徽商之心如此。他的诚信行为应该是和“理”的信仰有关的。而且这条资料也为上一节论商人重视儒家“语录”增添一证。
但是民间信仰是三教混合的,所以“鬼神”的观念有时也和“天”或“理”有同样的效用。明末江苏洞庭山金汝鼐(字观涛,1596~1645) 之例可为说明。汪琬《观涛翁墓志铭》引其子之言曰:
凡佐席氏者三十年……席氏不复问其出入,然未尝取一无名钱。所亲厚或微讽曰:君纵不欲自润,独不为子孙地耶?翁叱之曰:人输腹心于我,而我负之,谓鬼神何?……有寄白金若干两者,其人客死无子,行求其婿归之。婿家大惊,初不知妇翁有金在吾父所也。故山中人皆推吾父长者。
文集方志中这一类诚信不欺的事迹太多,举不胜举。以下就汪道昆《太函集》中择数例以说明商人和道、释二教的关系。《太函集》卷十四《赠方处士序》记盐商方彬(字宜之) 以重然诺而著义声,晚年则归向道教。其文略云:
季年喜黄老,筑舍七宝峰下,与双鹤道士俱。客讽之曰:处士以贾豪,奈何近方士?处士笑曰:吾仆仆锥刀之末,终不欲老市井中,诚愿卒业玄同。幸而蝉蜕于污渎,足矣,恶用窃刀圭翔白日为也。夫一处士也,其始也,轻身而就贾,不亦豪举乎哉!及其以操行致不赀,盖节侠也。卒之游方外,归乎葆真,非达者宜不及此。
这很像上篇新道教所说的神仙下凡历劫,在人间成就事业后再“归正位”、“成正果”。同书卷二八《汪处士传》记一位16世纪在上海经商成功的汪通保,其人是有操守而有“好仁义”之称的廉贾。其中有一段说:
处士尝梦三羽人就舍,旦日得绘事,与梦符,则以为神,事之谨。其后几中他人毒,赖覆毒,乃免灾。尝出丹阳,车人将不利处士,诒失道。既而遇一老父,乃觉之。处士自谓:幸保余年,莫非神助。乃就狮山建三元庙,费数千金。
这位汪通保显然深信他之所以能处处逢凶化吉是出于“神助”。又同书卷三五《明赐级阮长公传》记大贾阮弼的事迹。其人“雅以然诺重诸贾人,不言而信,其言可市。诸贾人奉之如季河东(按:季布) ”。《传》云:
季年崇事二氏,种诸善根。尝……缮三茅宫,饰诸神像,乐善而无所徼福,其费不赀。……长公故多阴德,务施恩于不报,加意于人所不及知。……族母私蓄数十缗,阴托长公取息。有顷,族母亡。长公握子母钱毕归其子。其子不知所出,力却之。长公语之故,稽首而后受。
汪道昆最后用“天报”的观念解释阮弼的成功曰:
要之,人能负长公父,而天报于长公;人能负长公,而天报于昌阜。
可见汪道昆本人也相信民间三教混合的“天”的观念。清初归庄在其《杂著》中记载了下列的故事:
丁未(按:康熙六年,1667年)春,杭州大火,延烧一万七千余家,惟有一家,岿然独存于四面灰烬之中。问其人,则业卖油者再世矣。惟用一称,虽三尺童子不欺之。余谓此事甚小,但即此一事观之,则其平生必每事诚实。当末世诈伪百出之时,而有此笃厚君子,得天之庇,宜哉!
归庄的“末世诈伪”乃隐指当时变节的士大夫,不是专对商人而发。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似乎确已接受了诚实不欺可“得天之庇”的民间信仰。这一点事实上并不足异。自南宋以来,《太上感应篇》一类的善书也同样对士阶层有深切的影响。南宋的真德秀、明末的李贽、焦、屠隆等都曾宣扬过此篇。清代经学大师惠栋(1697~1758) 且曾为此文作注。朱(1731~1807) 为惠注本作“序”有云:
忆予兄弟少时,先大夫每日课诵是书,即以教诸子。……其恂恂规矩,不敢放佚者,于是编得力焉。
汪辉祖(1731~1807) 《病榻梦痕录》卷上云:
检先人遗箧,得《太上感应篇》注,觉读之凛凛。自此晨起必虔诵一过。终身不敢放纵,实得力于此。(乾隆十年条)
同书卷下又记:
还先人遗愿,赴云栖建水陆道场。余素懵内典,读莲池大师(即宏,1535~1615)云栖法汇、竹窗随笔,事事从根本著力。乃知天下无不忠不孝神仙,成佛作祖,皆非伦外之人,实与吾儒道理,异室同堂。(乾隆五十八年条)
朱和汪辉祖都承认他们的“不敢放佚”是得力于《太上感应篇》。汪辉祖更进一步接受三教“异室同堂”之说。可见民间信仰并不专属于下层人民,而同样是上层士大夫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上层文化”(elite culture) 和“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 在中国传统中并不是截然分明的,其间界线很难划分。士大夫当然有他们的“上层文化”,但是他们同时也是浸润在“通俗文化”之中。不但中国如此,欧洲在1500年至1800年之间,据说贵族、僧侣也同样参加“通俗文化”中的许多活动。根据上面所引朱和汪辉祖的话,天地、鬼、神、报应等观念对他们的确发生了约束的力量,形成了他们的“第二文化” 。士大夫尚且如此,则商人更可想而知。把商人看成只知“孳孳为利”、毫不受宗教道德观念约束的一群“俗物”,在大量的文献面前是站不住脚的。
5.“贾道”
明代商人已用“贾道”一词,这似乎表示他们对商业有了新的看法,即在赚钱以外,还有其他的意义。但“贾道”又有另一层意思,即怎样运用最有效的方法来达到做生意的目的。这相当于韦伯所谓“理性化的过程”(the process of rationalization) 。韦伯在此特别重视清教伦理中所谓“天职”(calling) 的观念。西方资本家全心全意地赚钱,但他们赚钱并不是为了物质享受,因此依然自奉俭薄。依韦伯的解释,这些资本家的宗教动机是要用经营成功来证明自己在尽“天职”方面已“才德兼备”(virtue and proficiency in a calling) 。 此外当然也还有世俗的动机,如财富所带来的“权力”(power) 和“声誉”(recognition) 以及因能使无数人就业和家乡经济繁荣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等。
现在我们要问:明清中国商人的勤俭起家究竟是出于哪些动机呢?以世俗动机而言,中西商人大致相去不远,甚至中国人所谓“为子孙后代计”的观念在西方也并不陌生。更值得我们重视的倒是超越性的动机。明清商人当然没有西方清教商人那种特有的“天职”观念,更没有什么“选民前定论”,但其中也确有人曾表现出一种超越精神。他们似乎深信自己的事业具有庄严的意义和客观的价值。在本篇第二节,我们已引了15世纪山西商人席铭的豪语:“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于世,抑岂不能树基业于家哉!”在这句豪语的后面,我们隐然看到他对即将投身的商业抱有一种自傲的心理。士的事业在国,是“立功名于世”,然而商的“基业”在家,也足以传之久远。明末曹叔明《新安休宁名族志》卷一记商人程周有云:
贾居江西武宁乡镇……遂致殷裕,为建昌当,为南昌盐,创业垂统,和乐一堂。
此处所用“创业垂统”四字实在非同小可。这四个字从来是开国帝王的专利品,现在竟用来形容商人的事业了。这一新用法所反映的社会心理的变化是不容忽视的。汪道昆《明赐级阮长公传》也说:
先是长公将以歙为菟裘,芜湖为丰沛。既而业大起,家人产具在芜湖城内外,筑百廛以待僦居。……中外佣奴各千指,部署之,悉中刑名。
“菟裘”是用《左传》的典故:“使营菟裘,吾将老焉”(“隐公十一年”) ,指退休养老之地。但“丰沛”是汉高祖“创业垂统”的根据地,此处即借以指阮氏的商业基地。可证以创建帝业比喻大商人的事业经营在16世纪已相当普遍。试看阮氏商业的规模之大,布置之密,此“丰沛”一词确不是随便借用的。今天西方人所谓“商业帝国”(business empire) 的观念在中国早已出现了。《新安休宁名族志》卷一又有一条云:
黄球号和川,幼负大志,壮游江湖,财产日隆。娶城北金公红女,青年完节,克苦勤俭,佐子不逮。商贾池阳,家道大兴。
这“幼负大志”四字也是从来用之于士人的,现在又转移到商人身上来了。把这许多证据聚拢在一起,其所显示的历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可以说是“良贾何负于闳儒”的心理的一种表现。汪道昆《潘汀洲传》记潘氏“既老,属诸子为良贾,诸孙为闳儒” 。可见“良贾”和“闳儒”在他的价值系统中确已相差极微。不但当时商人如此想,士大夫也如此说。汪道昆《范长君传》曰:
司马氏曰:儒者以诗书为本业,视货殖辄卑之。藉令服贾而仁义存焉,贾何负也。
“服贾而仁义存”即发挥《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思想。钱谦益(1582~1664) 为江苏洞庭山的富商之子写传,也引司马迁语而引申之曰:“人富而仁义附,此世道之常也。” 其实这种说法恰与王阳明“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及沈“其业则商贾,其人则豪杰”等语消息相通。不但如此,汪道昆《虞部陈使君榷政碑》更说:
窃闻先王重本抑末,故薄农税而重征商,余则以为不然,直壹视而平施之耳。日中为市,肇自神农,盖与耒耜并兴,交相重矣。……商何负于农?
汪氏显然肯定商贾既不负于儒,也不负于农,他们所从事的也是正正当当的“本业”。他的说法不但远在黄宗羲“工商皆本”(《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之前,而且更为详尽透彻。他的薄征商税的主张在16世纪也是十分流行的。例如张居正(1525~1582) 和张瀚同持此见,后者在南京兼摄榷务时并曾实行过薄征政策。
由于商人自己和士大夫都开始对商业另眼相看,商业已取得庄严神圣的意义。王阳明说“四民异业而同道”,现在商人确已有其“贾道”了。因此商人也发展了高度的敬业和自重的意识,对自己的“名”、“德”看得很重。归有光《东庄孙君七十寿序》云:
昆山为县在濒海,然其人时有能致富埒封君者。近年以来,称贤者曰孙君。……自其先人……为人诚笃,用是能以致富饶。至孙君尤甚,故其业益大。然恂恂如寒士,邑之人士皆乐与之游。而以有缓急告者,时能恤之。于是君年七十,里之往为寿者,皆贤士大夫也。而予友秦起仁又与之姻,言于余,以为君非独饶于赀,且优于德也。
归有光此文暗用太史公《货殖列传》“君子富,好行其德”的笔法,以“德”字为这位孙姓富贾颂寿。这是一种极高的礼赞。昆山是人文极盛之地,而“贤士大夫”都肯为一位商人祝寿,仅此一点,即可见其人德望之隆。商人自己也非常重视“德”。汪道昆《吴伯举传》记大盐商吴时英的“掌计”(即今之经理之类) 假他的名义向其他商人借了一万六千缗,后来还不出来。有人向吴时英建议:“亦彼责,彼偿,尔公何与焉!”他答道:
诸长者挈累万而贷不知者何人,信吾名也。吾党因而为僭,而吾以僭乘之,其曲在我。是曰倍德;倍德不详。
最后这笔债还是由吴时英自己偿还了。这个例子最可证商人对“德”的重视和对“名”的爱惜。不但大贾如此,普通商人也是一样。姚鼐在1813年写的《赠中宪大夫武陵赵君墓表》记湖南商人赵宗海死后的情况说:
初君所受托以财贿者,有数千金。及君没,颇乏偿赀;或谋以孤寡辞而弗与。太恭人(按:宗海妻)曰:吾夫信义,故人托之。今弗偿,为夫取恶名也。乃破产鬻室中衣物以尽偿其负。
甚至“伙计”(或“夥计”) 也必须建立自己的声名,才有前途。明代沈孝思《晋录》(《学海类编》本) 说: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丐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少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为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
可见山西“伙计”的道德自律之严。新安的情形也是一样。顾炎武《肇域志》云:
新都……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其人铢两不私,故能以身得幸于大贾而无疑。他日计子母息,大羡,副者始分身而自为贾。故大贾非一人一手足之力也。
“副手”即前引《太函集》之“掌计”,这是徽州的“伙计”。其人必“铢两不私”,才能得到大贾的信任,然后再自谋发展。这两条资料当然是指一般的情况而言,“伙计”舞弊的事终是不可免的,上引吴时英的“掌计”即是一例。以徽州而论,其“副手”、“掌计”大抵以亲族子弟为多。王世贞(1526~1590) 《赠程君五十序》:
门下受计出子者恒数十人,君为相土宜、趣物候,人人授计不爽也。数奇则宽之,以务究其材;饶羡则廉取之,而归其赢。以故人乐为程君用。而自程君成大贾,其族之人无不沾濡者。
休宁金声(1598~1645) 《与歙令君书》也说:
夫两邑(按:休宁、歙县)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
这些证据都是说明“伙计”制度对明清“贾道”发展的贡献。“伙计”制在当时相当普遍,除上述山西、安徽外,江苏也有之。归庄《洞庭三烈妇传》记江苏洞庭山一个名叶懋的“伙计”的事,说:
凡商贾之家,贫者受富者之金而助之经营,谓之伙计。叶懋婚仅三月,出为同宗富人伙计。
可证江苏的“伙计”也多来自宗族或亲戚子弟之贫者。由于“伙计”制度对明清商业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扼要地指出其中几个特点。但限于篇幅及体例,详细的论证无法涉及。第一,这是一个全新而普遍的制度。以规模和组织言,以前中国史上实无前例,因此《晋录》和归庄才觉得有必要为“伙计”下一界说。 第二,以上引资料及其他个案来看,大贾和“伙计”断然是“老板”和“雇员”的关系。顾炎武所引资料说新安的“副手”后来可以“分身自为贾”,这不但与山西“伙计”的“获大利于后”相合,而且在《太函集》中实例甚多。我们不能因为偶有一个例子,即“掌计”太“跋扈”,欺负老主人,被青年力壮的少主人“面数而之庭下” ,便推断大贾和“伙计”是“主奴关系”或“封建土地关系在商业上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三,“伙计”、“掌计”大体都是亲族子弟。这一事实恰好说明明清商人如何一面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一面又把旧的宗族关系转化为新的商业组合。这正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一种过渡方式。清末民初中国新型的资本家仍然走的是这条路。难道现代型企业的发展必须以“六亲不认”为前提吗?试问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还有比亲族更可信托的“助手”吗?西方的宗教组织在社会上占主宰地位,而中国无之。以社会功能言,中国的亲族组织即相当于西方近代各教派的组织。例如教友派(Quakers) 的通婚必须限于派内。韦伯以为新教伦理的一大成就即在打破亲族的束缚,使家与商业完全分开。而中国则太重亲族的“个人”关系,没有“事业功能”(functional tasks或enterprises) ,因此经济发展受到限制。 这是由于他对中国史缺乏认识的缘故。明清大贾与“伙计”的关系即已向“事业功能”迈出了一大步。所以山西以诚实不欺著名的“伙计”才会成为其他大贾“争欲得之”的对象。不但如此,亲族关系妨碍现代企业之说根本便站不稳。据艾施顿(T.S.Ashton) 对18世纪初期英国钢铁工业的研究,铁业当时几全在教友派的控制之下,而其中重要的企业家都和创业的达比(Darby) 家族有亲族关系,包括儿子、族人、女婿、连襟等,还有少数人是其“伙计”(employees) 出身。而且这还不是例外。在工业革命初期的西方,企业和家族关系的结合(the union of business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是一个极为正常的现象。 总之,我们对“伙计”制度的出现应予以最大的重视,因为他们可以说是中国经营管理阶层(managerial class) 的前身。
“伙计”制度是应运而生的,因为当时有些大贾的商业已遍及全国。例如上文已提到的那位以“芜湖为丰沛”的阮长公,“其所转毂,偏于吴、越、荆、梁、燕、豫、齐、鲁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长公为祭酒,升降赢缩,莫不受成” ,其经营的规模可以概见。而且此中“祭酒”一词也极为流行,更可注意。这又是商人已夺得士大夫的尊号之一证。吴伟业《太仆寺少卿席宁侯墓志铭》记江苏洞庭山的席本桢(1601~1653) 的商业规模有云:
其于治生也,任时而知物,笼万货之精,权轻重而取弃之,与用事者同苦乐。上下戮力,咸得其任。通都邸阁,远或一二千里,未尝躬自履行。主者奉其赫蹄数字,凛若绳墨。年稽月考,铢发不爽。
这种组织的严密,仅凭一纸书信(“赫蹄”) 即可指挥至一二千里之外,较之现代企业何尝逊色?其“用事者”(“伙计”) 又何尝没有“事业的功能”?大贾必赖“伙计”,“非一人一手足之力”,这是一个实例。
**席本桢“读书治《诗》、《春秋》”,他做生意能“任时而知物”、“权轻重而取弃之”自然是拜儒家教育之赐。明清商人因多“弃儒就贾”,而且为贾后仍多不断地读书,他们的文化和知识水平并不在一般“士”之下。他们之擅“心计”并能掌握各地市场变化的规律,是和这一儒学背景分不开的。这一点现在已有研究者初步予以证实。 当时的商人“直以九章当六籍” ,这更说明商人对算术的重视。明末《商业书》中便往往附有《算法摘要》一类东西,以备商人参考。《指名算法》、《指名算法宗统》等商业算术书的大量出现尤其与商业发达有密切的关系。韦伯特别看重近代西方的复式簿记(double book-keeping) 和算术在商业上的应用,认为是“理性化的过程”的证据。中国虽无复式簿记,但16世纪的商业算术是足以和同时代的西方抗衡的。 现在让我们另举一些比较被忽略的证据以说明中国商业经营的“理性化的过程”。**顾宪成(1550~1612) 《小心斋札记》卷十四有一条云:
何心隐辈坐在利欲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有不可到处。耿司农(按:定向,1524~1596)择家僮四人,人授二百金,令其生殖。其中一人尝从心隐请计。心隐授以六字诀曰:买一分,卖一分。又有四字诀:顿买零卖。其人遵用之,起家至数万。
这个故事是否真,无关紧要。但由此可见知识对于经营商业的重要性。据清代档案,吕留良的孙辈在雍正十年(1732年) 发遣宁古塔为奴,但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 ,其曾孙等已因开药铺(这是吕留良的旧业) ,贩卖米、盐以及貂皮、人参等致富,并申请捐纳监生了。 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正可与何心隐的传说互证。何心隐的六字诀其实即是要转手快,薄利多销,也就是韦伯所说的“principle of low prices and large turnover” 。“薄利多销”事实上是明清商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指导原则,实例不胜枚举。以下我们只选几个最有代表的个案对此点略作说明。康海在《叔父第四府君墓志铭》中记载了他的四叔康銮对一个待高价而售货的商人的批评。康海引他的叔父的话并加以论断曰:
“彼不知贾道也。俟直而后贾,此庸贾求不失也,可终岁不成一贾。凡吾所为,岁可十数贾,息固可十数倍矣。”故长安人言善贾者,皆曰康季父云。
这里“贾道”两字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观点之上的,故“善贾”之“善”即是“工欲善其事”之善,在道德上原是中立的。这种“贾道”便是多做几次生意,每次少赚一点,不必等到高价才脱手。但从另一角度看,此道又是合乎道德的。魏禧《三原申翁墓表》说申文彩:
业盐,得廉贾五利之术,家以大昌。
“廉贾”语出《史记·货殖列传》:“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宫崎市定对这两句话有新解,认为是“贪贾”只跑三回生意,“廉贾”则跑五回。 其说若可信,则薄利多销的原则早已出现,不过到明清才大行其道。但“廉”字则有道德含义。汪道昆《明处士江次公墓志铭》记江氏戒其子之言曰:
且耕者什一,贾之廉者什一,贾何负于耕?古人病不廉,非病贾也。
所以,儒家的知识和道德在“廉贾”身上又获得了统一。上一节所引金汝鼐为舅父席氏做“伙计”,大获信任。汪琬《观涛翁墓志铭》续云:
翁善治生,他贾好稽市物以俟腾踊,翁辄平价出之,转输废居,务无留货而已。以故他贾每致折阅,而翁恒擅其利。
这是以薄利多销而获成功的典型例证。再举一个18世纪的书贾陶正祥(1732~1797) 之例。孙渊如《清故封修职郎两浙盐课大使陶君正祥墓碣铭》说他:
与人贸易书,不沾沾计利所得。书若值百金者,自以十金得之,止售十余金。自得之若十金者,售亦取余。其存之久者,则多取余。曰:“吾求赢余以糊口耳。己好利,亦使购书者获其利。人之欲利,谁不如我?我专利而物滞不行,犹为失利也。”以是售书甚获利。……当是时,都门售书画有王某,售旧瓷什器有顾某,意见悉如君,皆盛行于时。
这位书贾能对“薄利多销”发挥出一番大道理,正见其深入理性化的“贾道”。同时尚有王某、顾某也不谋而合,尤足为“贾道”盛行之证。
明清商人高度理性化使他们能转化许多传统文化资源为经营企业的手段。前面我们已讨论了他们怎样在亲族的基址上发展了“伙计”制度。现在再看下面的例子。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四《杂记下》云:
苏州皋桥西偏有孙春阳南货铺,天下闻名。铺中之物亦贡上用。案春阳,宁波人,明万历中,年甫弱冠,应童子试不售,遂弃举子业,为贸迁之术。始来吴门,开一小铺,在今吴趋坊北口。……其为铺也,如州县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总管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四十年……其店规之严,选制之精,合郡无有也。
这简直是现代百货商店的经营方式了。但最值得注意的则是孙春阳竟能把州县衙门的“六房”制度转化为经营南货铺之用。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当然是来自他的“弃儒就贾”的背景了。明清“贾道”的理性化也带来了新的竞争方式。19世纪上半叶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三“布利”条记:
新安汪氏设益美字号于吴阊,巧为居奇,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头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群誉布美,用者竞市,计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论匹赢利百文,如派机头多二万两,而增息二十万贯矣。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嗣汪以宦游辍业,属其戚程,程后复归于汪。二百年间,漠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
傅衣凌引此条,认为这是类似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大致是不错的。 益美布号凭布头的商标给银二分即是西方的rebate,所不同者,似乎是给缝衣匠,而非直接还给顾客而已。这种广告方式显然也是当时“贾道”的一种新发展。
6.结语
本篇关于16至18世纪商人的社会地位和意识形态的研究使我们看到这三百年间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都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从社会史的角度看,商人的“睦任之风”已使他们取代了一大部分以前属于“士大夫”的功能(如编写族谱,修建宗祠、书院、寺庙、道路、桥梁等) 。商人社会功能的日益重要也反映在政府对他们的态度上。清代政府不但对商人的控制已较为放松 ,而且态度上也较为尊重。故至晚在19世纪以后,政府的公文告示中已绅、商并提。在商业发达的地区“商”有时尚在“绅”之前。例如麟庆(1791~1846) 自述他1823年任徽州知府事,曾说:
余抵任后……即出示严禁棚民开垦山田;劝谕商、绅,疏通河道,以妨壅遏。
这当然是因为徽州商人的财力特别雄厚之故。士大夫对商人的改容相向也是一个极不寻常的社会变化。16世纪以后著名文士学人的文集中充满了商人的墓志铭、传记、寿序。以明、清与唐、宋、元的文集、笔记等相比较,这个差异是极其显著的,这是长期的“士商相杂”的结果。本篇所引的李梦阳、康海、汪道昆以迄清代的许多作者,或出身商贾之家,或与商贾有姻亲,或与之相交游。因此他们不但记述了商人的活动,而且有意无意之间为他们的利益说话。这正如19世纪不少美国牧师和作家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作辩护一样。这些人也都是工商企业家的子弟、亲戚或朋友。
从思想史的观点看,新变化也极为可观。儒家的新四民说以及理欲论和公私观上的新论点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最可注意的是商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出现。在明代以前,我们几乎看不到商人的观点,所见到的都是士大夫的看法。但是在明、清士大夫的作品中,商人的意识形态已浮现出来了,商人自己的话被大量地引用在这些文字之中。如果全面而有系统地加以爬搜,其收获必极为丰富。更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士商相杂”,有些士大夫(特别如汪道昆) 根本已改从商人的观点来看世界了。明、清的“商业书”虽是为实用的目的而编写,其中也保存了不少商人的意识形态,那更是直接的史料了。我们尤应重视商人的社会自觉。他们已自觉“贾道”即是“道”的一部分。商贾“虽与时逐,而错行如四时;时作时长,时敛时藏。其与天道,盖冥合也” 。因此他们自然也可以“创业垂统”。一般的商人固然是“孳孳为利”,正如一般的士人也是为“利禄”而读书一样,但其中也有一些“幼有大志”的商人具有超越性的“创业”动机。他们同样重视自己的“名”、“德”或“功业”。在中国自古相传的“三不朽”中,他们至少可以希望在“立功”和“立德”两项上一显身手。
商人恰好置身于上层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接榫之处,因此从他们的言行中,我们比较容易看清儒、释、道三教究竟是怎样发生影响的,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一般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有两极化的倾向:或者偏向“纯哲学”的领域,或者偏向“造反宗教”。这是有意或无意地把西方的模式硬套在中国史的格局上面。在这两极之间,还有一大片重要的中间地区仍是史学研究上的空白。商人的意识形态在这一中间地区实占有枢纽性的地位。思想自然并不是一切,但人的活动则未有不受思想支配的。商人也不可能例外。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论旨也许强调得过头了,他对于中国宗教的论断更缺乏事实的支持,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很有意义的。本篇的主旨之一便是要发掘出明清商人的精神凭借何在。他们在经营上的成功当然有赖于许多客观的因素,这是现代社会经济史家热烈讨论的对象。本篇则取“人弃我取” 、“相辅相成”之意,希望找出商人究竟是怎样巧妙地运用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文化因素来发展“贾道”的。整个地说,他们确能“推陈出新”。我们决不能因为他们依附了某些旧形式而忽视其中所涵蕴的新创造,前面所论及的“伙计” 制便是一个显例。
我们也决不能夸张明清商人的历史作用。他们虽已走近传统的边缘,但毕竟未曾突破传统。他们所遭到的主要阻力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必须另有专文研究,此处无法全面讨论。但是我们愿意提出一点来略加阐明。
韦伯研究西方古代的经济发展,曾提出一个看法,即自由商业在“共和城邦”中易于发展,在君主专政的官僚制度下则常遭扼杀,因为后者以“政治安定”(political stability) 为主要目标。 这一论点所蕴涵的前提是政治结构有时也可以对经济形态发生决定性的作用。这个看法似乎能够部分地解释明清商人的困境。有些学者已注意到明清的“君主独裁” 或“国家与官僚” 对商人的影响。以盐商为例,他们一方面固受君主专制下官僚体系的保护,但另一方面这个体系又构成他们发展的终极限制。如所周知,明清商人有下贾、中贾、大贾的分化。一旦到了大贾的地位,他们每年对政府便要有种种“捐输”,至于贪官污吏的非法榨取则更不在话下。盐商诚然表现了浓厚的政治兴趣,如捐官、交结公卿权贵、附庸风雅等都是明证,但这些只是表面现象;分析到最后,他们的政治投资还是为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前面已引李梦阳语,扬州盐商的“奢”如畜声乐、妓妾、珍物等只为了“援结诸豪贵、藉其庇荫”。一般中贾也同样受政府和官僚的牵累。19世纪甘肃省的“发商生息”便最为病民之政。有些州县官甚至将发商本银一概吞没,以致承领各商只好逃亡。 小贾的命运也同样可悲。明末《士商要览》卷三《买卖机关》中有一条为“是官当敬”。其下注曰:
官无大小,皆受朝廷一命,权可制人,不可因其秩卑,放肆侮慢。苟或触犯,虽不能荣人,亦足以辱人,倘受其叱挞,又将何以洗耻哉!凡见长官,须起立引避,盖尝为卑为降,实吾民之职分也。
试看专制的官僚系统有如天罗地网,岂是商人的力量所能突破?“良贾”固然不负于“闳儒”,但在官僚体制之前却是一筹莫展了。
本篇既是思想史的研究,还是让我们引几位清代思想家的话来结束本文吧!顾炎武(1613~1682) 《郡县论·四》说:
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
戴震《汪氏捐立学田碑》有云:
凡事之经纪于官府,恒不若各自经纪之责专而为利实。
沈《谢府君家传》之末论曰:
兴造本有司之责,以束于例而不克坚。责不及民,而好义者往往助官徇民之意。盖任其责者不能善其事;善其事者每在非责所及之人。后世之事大率如此。此富民所以为贫民之依赖,而保富所以为周礼荒政之一也。
这三位思想家所讨论的都是关于政府控制和人民自治之间的利害得失的问题。顾炎武的话是原则性的通论,戴震和沈则分别针对富商立学田和修桥梁之事而发议,但三人的见解竟不谋而合。从本文所研究的时代背景着眼,这是特别足以发人深省的。
附录:士魂商才——《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日译本自序
我在本书中虽然强调了儒家伦理的重要作用,但是我所说的儒家是宋明以下的新儒家,其中已吸收了佛教的成分,特别是新禅宗的影响。宋明儒学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心性论,因此也具有明显的内倾性格。宋明心性论的最后根据当然是原始儒家的经典,特别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这部宋以后所谓《四书》都是在佛教进入中国以前撰成的,代表了中国本土的智慧。然而不可否认的,这一原始智慧的再发现和新发展是由新禅宗促成的。韩愈(768~824) 受了新禅宗的启示,因此才致力于重建儒家的道统。他和李翱(774~836) 两人共同提倡儒家关于心、性的学说。虽然他们(尤其是李翱) 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掉佛教的观点,但是他们的终极目的是要从佛教手中夺回儒家久已失去的阵地。因为从南北朝到隋唐这一长时期中,中国知识人大体上都相信儒家是只管“治身”的,也就是“世间”的学问,而佛教则是“治心”的,也就是“出世”的学问。“出世”比“世间”更为根本。
……
其次,本书的另一重点是讨论商人的精神。中国的商人阶层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便已出现在历史的舞台。秦汉以下,商人也一直都在社会上活跃。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特别重视明清的商人呢?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商和士之间的互相流动开始变得非常密切了,而另一方面商人阶层又明确地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ideology) 。换句话说,商人在中国的社会价值系统中正式地上升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渐渐转变为士、商、农、工的新秩序了。更值得注意的是,15、16世纪以来,许多“士”竟成为“商”的代言人:所谓商人的意识形态其实是通过“士”的笔或舌而建立起来的。甚至像王阳明这样的大哲学家、李梦阳这样的大文学家也开始给商人写墓志铭,并且说“四民异业而同道”或“士商异术而同心”了。王阳明以后,明清的重要文集中,常常可以找到有关商人的记载。中国的社会结构在不知不觉中已发生了一个很基本的变化。我在本书中曾列举了许多例证。但是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再补充一条极重要的资料。唐顺之(1507~1560) 在《答王遵岩》中说:
仆居闲偶然想起,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无,虽唐、汉以前亦绝无此事。
“屠沽细人”是小商人,但人人死后都有一篇墓志,这一普遍的现象最可以说明当时商人阶层的心理:他们不但已不再自惭形秽,而且相信自己和立功、立德、立言的大人物一样,也可以“不朽”了。唐顺之明说这是以前所绝无之事,更证明商人墓志的大量出现确是明代中期以后的新发展。唐顺之既对商人这样轻视,照理说他自己是不会给商人写墓志的了。可是有趣得很,他的文集中至少便有两篇商人的传记:一篇是为新安商人程楷(1469~1524) 所写的《程少君行状》(《荆川先生文集》卷十五) ,另一篇是为扬州盐商葛钦之的妻子所写的《葛母传》(《文集》卷十六) 。不用说,这两篇传记都是很恭维他们的。在《葛母传》中,作者更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葛母不但送她的儿子到南京去向湛若水问学,而且还出了数百金为湛若水在扬州建了甘泉书院。这件事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它为商人和儒学的关系提供了新证据。唐顺之的《文集》更证实了本书的基本论点。
15世纪以来,“弃儒就贾”是中国社会史上普遍的新现象。不但商人多从士人中来,而且士人也往往出身商贾家庭。所以19世纪的沈垚说:“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最近读到汉译本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我十分欣赏他所创造的“士魂商才”的观念。明清的中国也可以说是一个“士魂商才”的时代,不过中国的“士”不是“武士”而是“儒士”罢了。看来在中、日两国的近世史和现代史上,“士魂商才”是一个共同的重大课题,值得历史学家共同研究和互相印证。
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概论——《朱子文集》序
我的理想中的“知人论世”既不是给朱熹(1130~1200) 写一篇传略,也不是撮述其学术思想的要旨,更不是以现代人的偏见去评论其言行。我所向往的是尽量根据最可信的证据以重构朱子的历史世界,使读者置身其间,仿佛若见其人在发表种种议论,进行种种活动。由于读者既已与朱子处于同一世界之中,则对于他的种种议论和活动便不至于感到完全陌生。不用说,这只能是一种高悬的理想。事实上,即使没有后现代史学的挑战,我们也早就知道历史世界已一去不返,没有人具此起死回生的神力了。然而不可否认,一直到目前为止,这一重构的理想仍然诱惑着绝大多数的专业史学家,甚至可以说,这是他们毕生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辛勤爬搜的一个最基本的动力。史学家诚然不可能重建客观的历史世界,但理论上的不可能并不能阻止他们在实践中去作重建的尝试。这种尝试建立在一个清醒的认识之上:历史世界的遗迹残存在传世的史料之中,史学家通过以往行之有效和目前尚在发展中的种种研究程序,大致可以勾画出历史世界的图像于依稀仿佛之间。同一历史世界对于背景和时代不同的史学家必然会呈现出互异的图像,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图像可以成为最后的定本。
……
概括言之,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高潮出现在仁宗之世,可称之为建立期。所谓建立期是指宋初的儒学复兴经过七八十年的酝酿,终于找到了明确的方向。在重建政治、社会秩序方面,仁宗朝的儒学领袖人物都主张超越汉、唐,回到“三代”的理想。这一理想也获得皇帝的正式承认,所以南宋的史浩向孝宗说:“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是仁宗以来“祖宗之家法”。(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 在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的共同意识方面,范仲淹所倡导的士大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呼声则获得了普遍而热烈的回响。第二阶段的结晶是熙宁变法,可称之为定型期。这是回向“三代”的运动从“坐而言”转入“起而行”的阶段,也是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在权力世界正式发挥功能的时期。在神宗与王安石之间,这时出现了一个共同原则: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这是北宋政治史上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大原则,王安石因此才毅然接受了变法的大任。也正是在这一原则之下,王安石才可以说:士之“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文彦博才可以当面向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程颐才可以道出“天下治乱系宰相”那句名言。尽管以权力结构言,治天下的权源仍握在皇帝的手上,但至少在理论上,治权的方向(“国是”) 已由皇帝与士大夫共同决定,治权的行使更完全划归以宰相为首的士大夫执政集团了。
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
引言
15、16世纪儒学的移形转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大体言之,这是儒学的内在动力和社会、政治的变动交互影响的结果。以外缘的影响而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弃儒就贾”的社会运动和专制皇权恶化所造成的政治僵局。这二者又是互相联系的:前者以财富开拓了民间社会,因而为儒家的社会活动创造了新的条件;后者则堵塞了儒家欲凭借朝廷以改革政治的旧途径。这两种力量,一迎一拒,儒学的转向遂成定局。以下试就新获史料提出几点具体的论证。读者倘取与《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及《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一并读之,则更可了解本文的宗旨所在。
(一)科举名额与“弃儒就贾”
“弃儒就贾”作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运动首先与人口的增长有关。我在《商人精神》一书中曾指出,明代科举名额——包括贡生、举人和进士——并未与人口相应而增加,士人获得功名的机会于是越来越小 。16世纪时已流行着一种说法:
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
这当然不是精确的数据,但它在社会心理上所产生的冲击力则甚大,足以激动不少士人放弃举业,献身商业。据人口史研究者的大略估计,14世纪末中国人口约为六千五百万,至1600年时则已在一亿五千万左右,增长了一倍多。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弃儒就贾”与科举名额的限制有关。但是如果要进一步证实这一假设,我们还必须找到直接的证据,进一步证明科举名额确已应付不了士人数量的不断增长。因为这既是一个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当时的人似不可能完全视若无睹。最近遍检16世纪有关文集,果然发现了下面两条重要的材料。
文徵明(1470~1559) 《三学上陆冢宰书》云:
开国百有五十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学校廪增正额之外,所谓附学者不啻数倍。此皆选自有司,非通经能文者不与。虽有一二幸进,然亦鲜矣。略以吾苏一郡八州县言之,大约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贡不及二十,乡试所举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众,历三年之久,合科贡两途,而所拔才五十人。夫以往时人材鲜少,隘额举之而有余,顾宽其额。祖宗之意诚不欲以此塞进贤之路也。及今人材众多,宽额举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几何而不至于沉滞也。故有食廪三十年不得充贡,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补者。其人岂皆庸劣驽下,不堪教养者哉!顾使白首青衫,覉穷潦倒,退无营业,进靡阶梯,老死牖下,志业两负,岂不诚可痛念哉!比闻侍从交章论列,而当道竟格不行。岂非以不材者或得缘此幸进,而重于变例乎?殊不知此例自是祖宗旧制,而拔十得五亦古人有所不废。岂可以一人之故,并余人而弃之。
陆冢宰是陆完,据《明史·七卿年表二》,他任吏部尚书在正德十年至十五年(1515~1520) 。又据开头几句贺语,知此书作于陆完初接任时,即1515年。文徵明所讨论的是苏州地区的生员名额和贡、举两途三年总数之间的比例。以一千五百名生员,三年之间只有五十人可以成为贡生或举人,则每一生员在三年之中只有三十分之一的成功率。可见“士而成也十之一”的估计是太保守了。此书中有两点应该特别解释一下。第一,“学校廪增正额之外,所谓附学者不啻数倍”这句话最能说明士的人口激增。《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一》云:
生员虽定数于国初,未几即命增广,不拘额数。宣德(1425~1434)中定增广之额。……增广既多,于是初设食廪者谓之廪膳生员,增广者谓之增广生员。及其既久,人才愈多,又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谓之附学生员。
现在苏州地区的生员,附学者已比廪、增两项正额多出了好几倍,足见士的人口增加之速。这也间接地反映了明代人口总额的大幅度上升。至于尚未成生员的士人,其数量自然更大得惊人,不过我们已无从估计了。第二,文徵明在此书中所要求的是增加贡生的名额。书中又有“比闻侍从交章论列,而当道竟格不行”之语,则当时朝廷上主张增贡额的大有其人,并不是文徵明一个人的主张。
与文徵明同时的韩邦奇(1479~1556) 也关心贡生长期沉滞、老死牖下的问题。他指出县令是最重要的治民官,而明代县令则分出于进士与举贡二途。前者因少年往往得志,为前途计,初出治民较能尽心;后者则垂老始得一官,“日暮途远,必为私家之计”。为了老百姓着想,他主张大增举人、进士的名额,以解决举贡一途的过度壅塞。因此他说:
岁贡虽二十补廪,五十方得贡出,六十以上方得选官,前程能有几何?不有以变通之,如天下斯民何!莫若多取进士,每科千名,乡试量其地方加之,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五之一。庶乎无偏无党,而治可成矣。
可见他和文徵明所关注的同是当时科举制度已无法容纳士的人口激增的问题,不过他的解决方案与文徵明不同而已。根据这两条史料,人口倍增与“弃儒就贾”之间的因果关联便完全成立了。
“弃儒就贾”蔚成风气以后,商人的队伍自然随之扩大了。限于史料,我们不可能对商人人口的增长提出任何数据,甚至约略的估计也无从着手。从有关文献出现的时代推断,我们大致可以说,“弃儒就贾”在16、17世纪表现得最为活跃,商人的人数也许在这个时期曾大量地上升。提及晚明的商人,我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徽商,其次则是山西商人。此外江苏洞庭的商人也很有名,当时已有“钻天洞庭遍地徽” 的谚语。其实16世纪时商人在中国各地都显出蓬勃的活力,张瀚(1511~1593) 的《商贾记》便是明证 。由于商人的社会活动在当时特别引人注目,故晚明小说中往往以商人为故事的主角,不但久已行世的《三言》、《二拍》如此,而且最近重新发现的《型世言》也是如此 。这也可以看作是商人数量在此期内激增的一个折影。
“弃儒就贾”为儒学转向社会提供了一条重要渠道,其关键即在士和商的界限从此变得模糊了。一方面是儒生大批地参加了商人的行列,另一方面则是商人通过财富也可以跑进儒生的阵营。关于前一方面我们已认识得很清楚,不必再说。关于后一方面,我们所知较少,不妨略作补充。《型世言》第二十三回有一段话,写得很生动:
一个秀才与贡生何等烦难?不料银子作祸,一窍不通,才丢去锄头匾挑,有了一百三十两,便衣冠拜客,就是生员;身子还在那厢经商,有了六百,门前便高钉贡元匾额,扯上两面大旗。
小说家讽世之言,自不足据为典要。但当时确有类似的现象,故说故事的人才能顺手拈来,涉笔成趣(例证见后文) 。我们不难想像,在16、17世纪之际,文徵明所说的超出生员正额数倍的“附学生员”之中,已有商人子弟用一百三十两买得的,甚至他所重视的“贡生”也已有商人用六百两银子从地方官手上活动得来的。《型世言》的描写虽夸张却不背史实,点出了当时商人进入士阶层的一条最常用的途径。在明、清文集中我们常常读到商人背景的“太学生”或“国子生”的墓志铭。这便是因为贡生例入太学——国子监——为监生的缘故。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韩邦奇《国子生西河赵子墓表》云:
西河子讳瓘字汝完,姓赵氏,别号西河。……关内冯翊之朝邑、大庆关人也。未弱冠,入为县附学生,以朱子诗屡应秋试,补廪膳。甫五年朝廷用辅臣议,令天下郡县选怀才抱德之士充岁贡。西河子应例上春宫,游国学,历部事。天官考勤,籍入仕版,选期已届,而西河子死矣。……西河子之乡,万余家皆习商贾,苦艰于息不益。西河子笑曰:何若是之艰哉!……世有无用之儒者哉!不数年起家数千金,而人莫窥其所自也。
韩邦奇是这位西河子的业师,《墓表》未提及其先世,可证赵原和其乡人一样,也是“习商贾”的,而且后来又以经商“起家数千金”。但是由于他已是监生的身份,故以“儒者”自居。从他的经历看,他恰恰是先为“附学生”,补上“廪膳生”,再“充岁贡”入国子监的。但我并不是暗示西河子取得“生员”的资格曾得力于一百三十两银子或他的“岁贡”是六百两银子买来的。他很可能是一个有才学的商人子弟,如他的老师在《墓表》中所叙述的。我举此例不过是为了证明16世纪的商人子弟确有从“附学生员”到“岁贡”入国子监的一条入仕之途。上引《型世言》的话在这个具体的例子中已获得充分的证实。最后我要指出,西河子以经商的成功来证明“儒者”并不是“无用”,这不但说明儒学已流入商人阶层,而且商人也将儒学看成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精神资源了。当时的人所谓“四民异业而同道”(王阳明语) 或“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李梦阳语) 在此都获得了印证。
(二)士商互动与价值观念的调整
明代中期以后士商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在《商人精神》中已有所论述。但该书专从商人方面着眼,而未多作推论。现在我想根据近年收集的若干资料,讨论一下士商合流与互动的一般状况,及由此而引发的价值观念的改变。本节所涉及的仅仅是资料中所显示的几个定“点”。这几个定“点”大致能够连系成几条“线”,但尚不足以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面”。这是我必须首先交代清楚的。
1.士商合流及其途径
李维桢不但极力想纠正“士大夫讳与贾人交”的传统偏见,而且更进一步鼓励大家心安理得地为商人作传。尽管新安贾人有生前交结宦官(当然限于少数人,其原因详见下文第四节) 和死后“行金钱谀墓”的风气,但一般的新安人则由于环境所逼才不得不投身商业。他特别引汉代“设科取士首孝弟力田”为典据,然后再说明新安人为什么不能“力田”,最后归结到新安商人的“材智气节”只能表现在“孝弟”上面。通过这样转弯抹角的论证,他终于获致一个自以为是确切不移的结论:以“孝弟”为唯一的“取士”标准,则新安商人是不折不扣的“士”,因此完全应该受到表扬。李维桢在此是用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表达“士商异术而同心”或“异业而同道”那种抽象的观念。但是他意识到儒家传统偏见的强固和同时士大夫对他“受取金钱”为富商大贾“谀墓”的批评,因此才用这一番委婉曲折的话来给自己开脱。与本文以下各节所论合起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李维桢的话代表了一部分士大夫的新观点,不能全以饰词视之。
2.从“润笔”的演变看儒家辞受标准的修改
李维桢为富商大贾写墓碑而“受取金钱”,其事竟载之《明史》,这象征了价值观念上的一大改变。如《蒋次公墓表》所云,同时王世贞和汪道昆也特以此见称于世。文人谀墓取酬,自古有之,但为商人大量写碑传、寿序,则是明代的新现象。因此,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明代文人“润笔”观念的转变。
3.商人“自足”世界的呈现
以上论士大夫为商人树碑立传都是富商大贾的事。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论证一般小商人也闻风而起,以致碑传泛滥。如果说树碑立传的儒家文化向来是由士大夫阶层所独占的,那么16世纪以后整个商人阶层也开始争取它了。现存明清商人碑传只是流传下来的极小部分,因为绝大部分都藏在私家,并未刊刻 。但当时碑传的大量产生是和商人热心表扬其父祖有密切关联的。这一现象已引起同时人的注意。
……
在传统中国社会,商不如士的关键主要在于荣誉——社会的承认和政治的表扬。但明代中晚期以来,商人也可以通过热心公益之举而获得这种荣誉了。前引王世贞《江阴黄氏祠记》,这个祠便是江阴人后来为报答黄宗周筑城、捐金助军、赡济贫民等善举而建立的,并且是“请之天子,下礼官议,报可而后行”的(页一八~一九) 。
我们已指出商人子弟入太学,未必都志在入仕,其中也有人是为了取得太学生的资格,以便利商业的运作。其实商人子弟即使入仕也往往别有怀抱。始举正反两例以明之。先说反面的例子。叶权(1522~1578) 告诉我们一个商人做官的真实故事如下:
余相识一监生,故富家,拜余姚县丞,缘事罢归,居常怏怏。余戏而劝之曰:公,白丁,以赀官八品,与明府分庭,一旦解官,家又不贫,身计已了,何不乐也?丞以情告曰:自吾营入泮宫,至上纳费金千两,意为官当得数倍。今归不勾本,虽妻子亦怨矣。呜呼!以勾本获赢之心为民父母,是以商贾之道临之也。卖爵之弊,何可言哉!
这位商人纳费千金才买得监生,比前引《型世言》所说的“六百两银子”还要多。但是他营谋地方官是从做生意的观点出发的,他并不认为做官是很荣耀的事。换句话说,在有些商人的眼中,官位也已经商品化了。
正面的例子是李维桢的《董太公家传》。董太公是河北大名府的巨商,其子董汉儒(《家传》中的“观察”,即地方司道官的古称) 则由科第入仕途。《家传》云:
久之,观察以高第应征,当授台省(即都察院)。太公私念:台省者,与天子执政相可否,脱不当,责四面至矣。已而除计户郎(即户部郎中),乃大喜。既榷税吴关,太公敕以蠲苛政宽商。商更辐辏,所入浮故额。
董汉儒最早由地方官调入中央的职位可能是都察院的十三道监察御史。这是纠察政事得失的言官,明代许多名臣都由此出身。但御史可以参与廷议,与皇帝、内阁接近,处于政治风暴的中心。董太公不愿其子冒风险,故闻董汉儒由都察院转调户部则为之“大喜”。后来董汉儒主管吴关税务,太公更特别叮咛他行“宽商”之政。很显然的,户部和税关都是可以对商人发生保护作用的衙门。董汉儒是和张瀚同时代的人,后者也出身商人世家,所以两人的经历恰可互相参证,以见商人的影响力已开始在政治上露面了。张瀚说:
余……兼摄(南京)上、下关抽分,余谓征商非盛世之政,弛十之二。商贩悦趋,税额较前反增十之五。
此二事若合符节,绝非偶然。我们不能因此便说,董汉儒、张瀚等人代表了商人阶层的利益。不过我们可以说,具有商人背景的士大夫,由于对商人阶层的疾苦有比较亲切的体认,他们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多少发生了一些“宽商”的效果。 儒家重农轻商的传统原则也因此不能不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有所调整。
概括言之,16世纪以后商人确已逐步发展了一个相对“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立足于市场经济,但不断向其他领域扩张,包括社会、政治与文化;而且在扩张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其他领域的面貌。改变得最少的是政治,最多的是社会与文化。其理由不能在此详说,因为这是必须另作研究的专题。这里应该提及的是:士商合流是商人能在社会与文化方面开辟疆土的重要因素。儒学适于此时转向,绝非偶然。
商人既已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自足”世界,他们便不可能在精神上完全是士大夫的“附庸”。这是为什么我要对商人精神生活“士大夫化”的旧说提出质疑,因为这是从士大夫的立场上观察历史所得到的结论。如果从商人的立场出发,我们毋宁说,他们打破了两千年来士大夫对于精神领域的独霸之局。即使我们一定要坚持“附庸风雅”之说,我们也无法否认下面这个事实:即由于商人的“附庸”,士大夫的“风雅”已开始改变了。儒家的“道”也因为商人的参加——所谓士商“异业而同道”——而获得了新的意义。即以墓志铭为例,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它已不再是士大夫的专利品,整个商人阶层都要求分享这一专利了。诚如唐荆川所讥讽的,甚至“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用现代的话说,他们也毫不犹豫地肯定自己的社会存在和价值了。张瀚说:“若有德业,则为铭。”现在则是大大小小的商人都认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同样有传之后世的价值。“德业”这两个字的社会含义也不得不随之扩大了。
如果我们继续保留商人“士大夫化”的概念,那么我们也必须增加另一个概念,即士大夫的“商人化”。这在明清语言中本是同时出现的,即“贾而士行”和“士而贾行”(或“商而士”和“士而商”) 。但是应该指出,明清时代流行的这一对概念还不免带有道德判断的意味。“贾而士行”是褒词,“士而贾行”则是贬义了。今天我们无论说商人“士大夫化”或士大夫“商人化”都只限于客观描述,在道德上是完全中立的。上面讨论文人“润笔”所涉及的辞受标准的修改,便是“商人化”的一个具体例证。士大夫“商人化”在当时也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社会现象,不但小说、戏曲的流行与之有关,儒家社会思想的新发展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商人化”的刺激。这是下一节将举例说明的。明、清的“士世界”和“贾世界”是互相交错的,士大夫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接触到商业化潮流所带来的社会变动。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对从社会到个人的种种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因而也加速了儒学的转向。
(三)儒家社会思想的新发展
明清儒家在社会思想上的新发展,我已先后多有论述,此处概不重复。 下面要介绍的两个观念是我最近研究的结论。但这只是过去研究的延伸和扩大,而不是独立自足的单元。特先声明,以免读者误会明清儒家社会思想的新发展仅止于此。
1.义利之辨
儒家义利之辨远始于孔子。《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首先用义与利来划分“君子”与“小人”。君子与小人最早是社会地位的分别,孔子则赋予以道德的含义,即“德”重于“位”。《论语》及后世文献中“君子”与“小人”也还有兼指“德”与“位”的,但儒家理论中则强调“德”的一面。 就道德意义说,儒家大致认为义利之分即公私之分。君子以公为心,故喻于义,小人以私为念,故喻于利。孟子、董仲舒以至宋儒大致都继承并发挥这一说法。宋代只有陈亮反对义与利互不相容,因而与朱熹之间发生了一场激辩。朱熹与陆九渊宗旨虽异,在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所以,象山在白鹿洞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极为朱子所赏识。下逮明代,王阳明仍循传统儒家之见。他没有正面讨论过义利的问题,但在《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的末段则痛斥“功利之见”。可见他的想法和朱、陆相去不甚远。
从孔子到王阳明,儒家义利论有两个主要特征:(1) 它是针对士以上的人(包括帝王) 而立说的,因为他们是对于公共秩序的直接负责者。至于孟子所谓“鸡鸣而起,孳孳为利”的一般人民(包括商人在内) 至少并不是儒家义利论的主要的立教对象。(2) 义与利基本上是互不相容的,人或者选择“义”,或者选择“利”,而不能“义利双行”(朱熹驳陈亮语) 。所以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大致与“理”与“欲”、“公”与“私”相同。
但是16世纪以后,“义利”的观念,也和“理欲”、“公私”一样,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前引韩邦奇《国子生西河赵子墓表》中,有一段作者自己的议论如下:
圣贤匏瓜哉!傅说之版筑,胶鬲之鱼盐,何其屑屑也。古之人惟求得其本心,初不拘于形迹。生民之业无问崇卑,无必清浊,介在义利之间耳。庠序之中,诵习之际,宁无义利之分耶?市廛之上,货殖之际,宁无义利之分耶?非法无言也,非法无行也,隐于干禄,藉以沽名,是诵习之际,利在其中矣。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人,是货殖之际,义在其中矣。利义之别,亦心而已矣。
这番议论的主旨在于说明义利之辨不是士所能独占的,对于商人也同样适用。故首举殷周之际的商贾胶鬲为例,以见古人并不以义专属之士。下迄明代,更是如此。士于“诵习之际,利在其中”,而商于“货殖之际,义在其中”。韩邦奇在这里扩大了义利之辨的社会含义,承认“孳孳为利”的商人也同样可以合乎“义”。这显然是对传统的义利观念予以新的诠释。但这一新说并非始于韩邦奇,比他稍早的商人已先有类似的见解。李梦阳(1473~1529) 《明故王文显墓志铭》说:
文显(按:名现,1469~1523)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
王现卒于嘉靖二年(1523年) ,次年二月下葬,李梦阳的墓志铭当即成于文显卒年。这篇铭文相当有名,韩邦奇似乎受了它的影响。无论如何,韩《表》论“货殖之际,义在其中”即是李《铭》所谓“利以义制”,而“利义之别,亦心而已矣”更与“商与士异术而同心”若合符节。《铭》的文字自然是李梦阳的,但思想则是王文显本人的。《墓志铭》说他“为士不成,乃出为商”,而其父又是教谕,他能对义利说别出新解,是不必惊异的。
这个新的义利观并不是偶然一现于16世纪,后无嗣响,而是持续有所发展的。17世纪初年顾宪成(1550~1612) 为他的一位同乡商人倪珵(1530~1604) 写《墓志铭》,其铭曰:
以义诎利,以利诎义,离而相倾,抗为两敌。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相成,通为一脉。人睹其离,翁(倪)睹其合。此上士之所不能訾,而下士之所不能测也。
顾宪成此《铭》的重要性在于它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传统义利观和明代新义利观之间的区别:前者是“义利离”,后者则是“义利合”。这一判断显然是受到魏晋时代“才性离”、“才性合”的启示。正因如此,新旧两种观点之间的界线才第一次得到最明白的划分。顾宪成自己的立场更显然是站在“合”的一边。从前面所引韩邦奇和李梦阳的文字,我们知道这一新观点酝酿已久。但由于顾宪成是思想家,他在寥寥数句中已将以前文学家的感性语言转化为较精确的哲学语言。“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相成,通为一脉”可以看作是新义利观的一个扼要的哲学界说,其中“主”、“佐”、“合”、“通”几个字都是颇费斟酌的。现代的读者也许会觉得这里只有结论而无论证。但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特色之一,不足为顾氏病。
顾宪成当然有可能读过韩、李之文,但他对义利的新思考并非完全根据前人的文字而来。更重要的是他的生活体验。他的父亲顾学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的长兄性成、仲兄自成也都先后佐其父经商。所以他是在商人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深知商业世界中同样有义与利的问题。 现在他公然抛弃了“义利离”的儒家旧解,而别倡“义利合”的新说,对这一转向我们不能不予以最大限度的重视。
最后,让我们再引一段18世纪初年的资料,以见新义利说的流传情况。张德桂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 为北京的广东商人所建立的仙城会馆撰写了一篇《创建记》,其下半篇畅谈义与利的问题。《记》曰:
兆图李子、时伯马子谒余请《记》。余问二子,厥馆所由。李子曰:由利。乡人同为利,而至利不相闻,利不相谋,利不相一,则何利?故会之。会之,则一其利,以谋利也,以是谓由利也。马子曰:由义。乡人同为利,而至利不相闻,利不相谋,利不相一,则何义?故会之。会之,则一其利,以讲义也,以是为由义也。夫以父母之赀,远逐万里,而能一其利以操利,是善谋利也。以为利,子知之,吾取焉。抑以乡里之俦,相逐万里,而能一其利以同利,是善笃义也。以为义,子知之,吾重取焉。然而利与义尝相反,而义与利尝相倚者也。人知利其利,而不知利自有义,而义未尝不利。非斯馆也,为利者方人自争后先,物自征贵贱,而彼幸以为赢,此无所救其绌,而市人因得以行其高下刁难之巧,而牙侩因得以肆其侵凌吞蚀之私。则人人之所谓利,非即人人之不利也耶?亦终于忘桑梓之义而已矣。惟有斯馆,则先一其利而利得也,以是为义而义得也。夫是之谓以义为利,而更无不利也。二子其即以此书之石,以诏来者,俾永保之。而义于是乎无涯,而利于是乎无涯。
此《记》基本上即取“义利合”的立场。其大旨在强调商人如各逐其一己的私利而不相谋,则不仅无义可言,而且并其利亦终失之。相反地,如果以会馆为中心而求共同之利,则不但能成就义,而且还能满足每一个人的私利。所以作者说义与利似“相反”而实“相倚”;义中有利,利中也有义。由此可见,在新说中,以“公”“私”判划“义”“利”的儒家原始义并未丧失,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顾宪成所谓的“离而相倾,抗为两敌”,而是“合而相成,通为一脉”的了。明清以来,“公”与“私”的关系已从“离”转向“合”,“义”与“利”的关系也同有此转向,可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且为思想史的内在理路更添一证。但内在理路与外在的社会变迁是息息相关的。义利新说之所以兴起于16世纪,并持续发展到18世纪以后,其故不仅应求之思想史,同时也必须求之于社会史。
2.奢的社会功能
中国自古以来都崇俭斥奢,无待论证。虽然近人注意到《管子·侈靡》篇公开主张“莫善于侈靡”,但这种观点并未流传下去。 然而不早不迟,到了16世纪,竟出现了一种肯定奢侈的思想,陆楫(1515~1552) 《蒹葭堂杂著摘抄》中有以下一节重要的议论:
论治者类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予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者也。何者?势使然也。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故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若使倾财而委之沟壑,则奢可禁。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功易事、羡补不足者也。……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号为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郡之民至不能自给。……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或曰:不然。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故其民赖以市易为主,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宁复以市易相高耶。……然则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济之耳,固不专恃乎此也。长民者因俗以为治,则上不禁而下不扰,欲徒禁奢可乎?呜呼!此可与智者道也。
原文很长,所引略有删节。首先让我介绍一下这番议论在现代重新被发现的经过。四十年前两位社会经济史专家——在大陆的傅衣凌先生和在美国的杨联陞先生——不约而同地发现了陆楫此文的重要性。傅先生将全文引在他的《明代后期江南城镇下层士民的反封建运动》一文中,先师杨先生则在他的名篇《侈靡考》中将全文译成英文,以飨西方的同行 。傅、杨两先生对此文都很推重,前者把它比之于曼德维(Bernard de Mandeville) 的《蜜蜂寓言》(按: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Public Benefits,初刊于1727年) ,后者也承认它以最接近“经济分析”的方式提出了鼓励“消费”的主张。换句话说,他们两位都在这篇议论中看到了一种“现代的”精神。
傅、杨两先生的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在反奢侈传统源远流长的明代中国,陆楫居然转而为奢侈作公开的辩护,这不能不说是价值观念上一个重大的改变。这一转向确使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17、18世纪英国思想家对于西方传统中的“奢侈”(luxury) 观念的根本修正。西方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经过罗马及中古基督教,也发展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反奢、禁奢的思想传统。其间各阶段的持论虽颇不同,但大体都视“奢侈”为恶德,节俭才是美德。16、17世纪的英国清教徒仍持旧说不变,但在17、18世纪之交,由于贸易日益重要(尤其是对外贸易) ,不少英国思想家开始改变立场,不再从纯道德的观点评价“奢侈”了。傅衣凌先生所特别提到的曼德维即其中之一人。于是英国思想史上便出现了一个对于“奢侈”的观念进行“非道德化”的运动(demoralization of luxury)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思想转变,现代的研究者甚至用“sea change”(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来形容它。
陆楫反对禁奢的议论在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不少个别的论点和英国17、18世纪的新思潮也确有可以互相参证之处,虽详略精粗之间未可同日而语。业师杨先生指出陆楫发现个体与全体当分别论断,俭德施之于一人一家为美德,但施之于天下则适得其反。这正是英国新思潮中的一个主要观念,巴本(Nicholas Barbon) 的《贸易论》(Discourse of Trade,1690) 倡议于前,曼德维则畅发于后。其说大致以“奢侈”在个人是“恶德”(vice) ,但在整个国家则反为“美德”(virtue) 。富者在衣、食、住三方面的挥霍恰好为贫者创造就业的机会。曼德维更举一极端之例:偷窃(theft) 自是“恶德”,然而铁匠制锁的生意却因此为之兴旺。陆楫强调奢风先于市易,而不是市易造成奢风。这也与巴本的说法相似,即人的欲望、时尚、好珍奇之心是贸易兴起的真正原因。陆楫又以宁、绍、金、衢等地的尚俭为其致贫之源,并以吴、越之尚奢反证其所以繁盛。巴本和曼德维也都运用这一论证的方式:尚奢的社会,人民都生活得很好,尚俭的社会往往不能赡养其大多数的人口,至于陆楫的主旨在反对政府“禁奢”,而应该“因俗以为治”,则更和英国的主奢论者的意见若合符节了。
但是我们必须避免断章取义和牵强附会,这是中西思想比较中最易犯的谬误。陆楫出于中国的传统,明代也没有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因此他在思想上绝不可能突然一跃而达到和英国17、18世纪的崇奢论完全相同的境界。他仍相信“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他反对“禁奢”的目的则在于“均天下之富”,这就表示他仅仅是对中国的传统进行重要的修改,而不是要彻底推翻它。从这两点说,他和英国的崇奢论者不但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了。更重要的,英国崇奢论的背后一方面有一整套西方文化和思想系统,另一方面又处于截然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的现实之中。换言之,英国崇奢论必须放在整个西方哲学、宗教、社会的脉络中去求了解,其中一环套一环,牵一发而动全身。从17、18世纪的崇奢论发展到苏格兰学派的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如休谟和亚当·斯密) ,其过程极为复杂,牵涉到的问题也无穷无尽。因此我们不可能把陆楫的一言一语,孤立地和英国任何一个思想家的说法互相比附,而企图从其中归纳出任何普遍性的历史概括。上面的几点比较其实只是为了说明一个简单的意思:16世纪的中国,主要由于商业的空前发展,许多传统的(以儒家为主) 价值和思想都经历了重新评估,“奢”也是其中之一。而英国崇奢论的出现和发展也和商业(特别是国际贸易) 的兴盛有密切的关联。英国思想家即由此而逐步变传统为现代。这是中西历史上的一种平行现象,确有比较的价值。如果撇开19世纪中叶以下的历史不论,专就中国史本身论“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则16世纪自有其划时代的意义。至于中国的“现代”何以迟迟不能彻底突破“传统”的格局,这则是另一问题,不是本文所能讨论的。
纯从语言上说,中文的“奢侈”,固然可以翻译成英文的“luxury”,但从文化体系上说,二者的含义大有广狭之别,所占的位置和分量也迥不相侔。简言之,“luxury”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涵盖面和指涉面远比“奢侈”在中国为广大,资料也丰富得多,因此西方学人以此为研究对象的专论至多。上引陆楫的议论虽与传统的观点极相违异,故为现代学人所重视,但若把它仅仅看作是一个偶发的孤见,则它实不能和西方“luxury”的观念作比较。我们只有把它看作是当时整个儒学转向的一个构成部分,它的历史意义才能清楚地显现出来。就我所知,明清之际,治生、四民、贾道、理欲、公私、义利等观念都发生了变化,而陆楫也恰在此时提出关于奢俭的新说,这绝不是偶然的。同样的,西方自17、18世纪以来,尚奢论投射的影响力也遍及各不同领域中的观念,如于美德(virtue) 、恶德(vice) 、公民特质(civic virtue,包括马基雅维利以来的virtù) 、理性(reason) 、情感(passion) 、人欲(desire) 、公益(public benefits) 、私利(private well-being) 、自由(liberty) 、人性(human nature) 、贸易(trade) 、财富(wealth) 、消费(consumption) 等。这也是成套的思想转向,不能抽出其中任何一项作孤立的处理 。严格地说,比较思想史的研究首先必须着眼于这两大体系的整体变化。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陆楫的议论。陆楫这篇文字有一显著的特色,即完全根据现状进行分析,而并不引经据典。事实上,他的主张——从社会的观点反对禁奢——也很难在儒家经典中找到明确的依据。由此可见他对于当时社会有直接而深入的观察。这一点又和士商混而难分的情势有关。他的父亲陆深(1477~1544) 是有名的词臣,他自然应该属于士的阶层。但是他的曾祖父则是一个弃儒就贾的成功商人,祖父也“长于理财”,“鸡初鸣即起,率家人事生产” 。这一家世背景也有助于我们对陆楫此文的理解。他并不是为商人辩护,不过他的生活和商业世界至少有一部分是重叠的。
陆楫的崇奢论是否曾引起当时和后世的注意?这个问题,傅、杨两先生都没有提及。下引的材料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法式善(1753~1813) 《陶庐杂录》卷五引《推篷寤语》云:
今之论治者,率欲禁奢崇俭,以为富民之术。殊不知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亏则此盈,彼益则此损。富商大贾、豪家巨室,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正使以力食人者得以分其利,得以均其不平。孟子所谓通功易事是也。上之人从而禁之,则富者益富,贫者愈贫也。吴俗尚奢,而苏、杭细民,多易为生。越俗尚俭,而宁、绍、金、衢诸郡小民恒不能自给,半游食于西方。此可见矣。则知崇俭长久,此特一身一家之计,非长民者因俗为治之道也。予闻诸长者云。
这条笔记毫无疑问是陆楫原文的一个提要。《推篷寤语》的作者是李豫亨,他的另一部书《三事溯真》有王畿(1498~1583) 的序,则李豫亨当是16世纪中叶的人,与陆楫(卒于1552年) 并世而略后。 《推篷寤语》原书未见,但法式善的转录必无大误。末句说“予闻诸长者云”,好像是听前人说的,但细察遣词用字,则非见陆氏原文不可能写得成。这只有等将来找到《推篷寤语》原书时才能判定,姑且不论。重要的是这一摘要证实了陆楫的议论当时便有人欣赏,甚至辗转传述。法式善在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转录《推篷寤语》此条,更可证他也同情陆楫的见解。 事实上,到了18世纪,陆楫以奢济贫的说法已相当流行。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苏俗奢靡”条说:
苏郡尚奢靡……虽蒙圣朝以节俭教天下,大吏三令五申,此风终不可改。而亦正幸其不改也。……即以吾苏而论,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故圣帝明王从未有以风俗之靡,而定以限制者也。
顾公燮与法式善是同时代的人,未必读过陆楫的文字,但思路基本上与之相合。所以奢的社会功用在16世纪被发现以后,也像新义利观一样,一直传衍至18世纪,未曾中断。这也是明清儒学转向的一项清楚的指标。
最后我更要指出,以奢侈维持社会就业在18世纪下半叶已不仅限于儒生之间的议论,而且逐渐影响到地方以至中央的社会政策了。
(四)商人与专制皇权
以上论儒学转向大体以“弃儒就贾”的长期演变为背景,现在我想换一个角度,扼要地检讨一下专制皇权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16世纪以来,明代专制皇权的最大特色是宦官在皇帝默许甚至怂恿之下广泛地滥用权力,其结果不但朝廷与士阶层互相异化,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商人阶层的权益。
由于商人在社会上的长期活跃以及商业的巨大利润,皇帝也开始对商人发生了一种艳羡之情。据毛奇龄(1623~1716) 说:
宝和六店,宫中储材物处。……武宗尝扮商估,与六店贸易,争忿喧诟。既罢,就宿廊下。
不知道这位风流的正德皇帝(1506~1521) 是不是有意仿效汉灵帝(168~188) 扮作商贾与宫女在“客舍”中饮食戏乐的故事(这是京剧舞台上正德皇帝“游龙戏凤”的原型) 。无论如何,这幕闹剧反映了商人在当时的声势浩大,以致连皇帝也在游戏中演出了“弃权就贾”的一幕。但明武宗并不仅仅“扮商估”而已,他当真开起店来了。自正德八年(1513年) 始,他派宦官在京师和许多都市开设“皇店”,以种种方法科敛商人,而贵戚藩王也起而效尤。商人和市民怨声载道。但这一做法一直沿续到明亡为止。
万历时则开始了骚动全国的矿税和其他征榷,也都由宦官主持,其为害之大而深更远在皇店之上。《明史》说:“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卷三五《宦官二·陈增传》) 但首当其冲的自然又是商人。
尽管个别的商人对专制皇权的压迫采取种种不同的方式——如取媚、笼络、逃避、反抗等,但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集体对于专制政府是绝不信任而且深怀恐惧的,他们对于宦官所代表的横暴皇权更是深恶痛绝。下面让我各举一例对此作具体的说明。在明末所谓“商业书”中,下面这三条戒律尤具有典型的意义:
1.是官当敬。官无大小,皆受朝廷一命,权可制人。不可因其秩卑,放肆慢侮。苟或触犯,虽不能荣我,亦足以辱我。备受其叱挞,又将何以洗耻哉。凡见长官,须起立引避,盖尝为卑为降,实吾民之职分也。
2.倚官势,官解则倾。出外经商,或有亲友,显宦当道,依怙其势,矜肆横行,屏夺人财,为臧否,阴挟以属,当时虽拱手奉承,心中未必诚服。俟官解任,平昔有别故受谮者,蓦怀疑怨于我,必生成害,是谓务虚名而受实祸矣。……凡作客,当守本分生理,不事干求,虽至厚居官,亦宜自重,谢绝请谒,使彼此受益,德莫大焉。
3.少入公门,毋观囚罪。凡到司府州县巡检衙门,及水陆途中口岸处所,或见奸妇贼犯异常之事,切不可挤入人丛,进衙观看。恐问官疑人打点,漏泄机密,关门扑捉。或强盗受刑不过,妄指在近搪塞,苟遭其害,虽公断自明,亦受惊骇矣。
由于这几条反复出现在晚明的商人手册中,我们可以断定当时商人对政府衙门普遍地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心理。他们不可能完全不和衙门打交道,但一涉公门便难免有不测之祸。这便是上述三条商人戒律的历史背景。我最近恰好发现了一条碑刻史料,可以为上引的戒律作证。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 江南提刑按察使司在上海立《禁衙蠹乘参访巧织款案陷害盐商告示碑》,碑文引商人汪凤翔等诉冤之词有云:
自分寄旅孤商,远挟重资,兢兢自守,犹恐地□自开祸门。至于地棍衙蠹,自分两途,畏之真如蛇蝎。无奈商惧取祸,祸自寻商。此辈欺异商为孤雏,羡盐务为奇货,或不风起浪,或指鹿□作(按:空缺□当是马字,即指鹿作马),干证砌陷之毒,指不胜屈。即如上年访犯潘文元一案,与汪凤翔、毕恒泰从无半面,有何干涉?蓦然县差徐邦等踏门,奉宪拿人,一□锁炙饱欲,始知砌入文元款内被害。彼时欲据实辨明,惧与访款相左;欲照款登答,实则良心难昧。可怜有限脂膏,奚堪若辈敲剥?究竟脱免,身家无恙,而力存天理之被害,翻为桃僵李代之齑粉矣。所以异商之苦,朝不保夕,人人自危。
这一段话真是如泣如诉,说得沉痛之至。这虽是清初之事,但其弊沿自明代,绝无可疑。必须指出,盐商在当时是最有势力的富商,因此才能得到申雪的机会。至于一般商贩在各地受到衙门中人的诬陷和讹诈,恐怕便很难得到“少入公门”的戒律中所说的“公断自明”了。
在晚明宦官擅权之下,商人的遭遇则更为悲惨。让我举一个最著名的例子以概其余。陈继儒(1558~1639) 《吴葛将军碑》说:
万历辛丑(1601年),内监孙隆私设税官于江南津渡处。凡米盐、果薪、鸡豚之属,无不有税。参随黄建节者,憸夫也。隆昵而任之,乃与市侩汤莘、徐成等谋分垄断焉。吴人罢市,行路皆哭。义士葛成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响应。时建节方踞葑关税。一卖瓜者,其始入城也,已税数瓜矣。归而易米四升,又税其一升。泣则反挞之。适成等至,遂共击建节,毙之。……于是义声大震,从者益广。当事闻之惊,谋御之以兵。独太守朱公燮元曰: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召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且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又率僚属连骑入市,呼诸百姓而慰之。杖汤莘等而系之于狱,众皆悦服。成因请于太守曰:始事者成也。杀人之罪,成愿以身当之,幸毋及众也。遂请就狱。……既入狱,哭泣送之者万人。其以酒食相饷者,日以千计。辞不获,悉以散于诸囚。四方商贾之慕义者,醵百金遗之,坚却不受。曰:我罪人也,焉用诸?皆再拜而退。归而尸祝之,祠于江淮之间,称为将军而不名,至于今因之。
我之所以详引这一段碑文是基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这是对宦官征商税的实况的一个最生动的具体描述;其竭泽而渔的手段至卖瓜者的遭遇令人叹为观止。第二,成千上万的苏州商人和市民公开支持葛成(1568~1630) 所组织的集体抗议。这可以看作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集体对于专制皇权的正式表态。更值得注意的是陈继儒碑文撰于明末,但康熙十二年(1673年) 才刻石立于葛成墓祠之前,上距抗议行动(1601年) 已七十二年,距葛成之卒(1630年) 也已四十三年。经过了这样长的时间,而且朝代也已更换,当地的人仍然对这位社会领袖念念不忘,可见苏州市民包括商人在内确已发展了某种程度的公民意识。第三,碑文也反映了士大夫在政治上对市民和商人阶层抱着相当同情的态度。太守朱燮元对这件事的处置便是明证。碑文作者陈继儒和文末所提到的文震孟(1547~1636) 和朱国祯(1557~1632) 都是江浙地区最著名的士大夫(文与朱均曾任内阁大学士) 。他们都对葛成的义举十分钦敬。朱国祯在他的著作中(如《皇明史概》卷四四《大事记》及《涌幢小品》卷九“王、葛仗义”条) 更一再宣扬此事。葛的义声播于天下后世,颇得力于同时士大夫的称誉。在这一事件上,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士与商的政治联盟共同对抗宦官所代表的专制皇权。因为宦官孙隆征税的对象是商人,特别是中、下层的商贩。葛成的社会身份今已不可考,或许他是当时失业的织工之一,他领导的抗议群众大概也以失业织工为多。但织工失业是由于机户(中、小商家) 罢织。据官方事后调查报告,“机户杜门罢织”是因为“每机一张,税银三钱”。不但如此,当时“榷网之设,密如秋荼”,以致“吴中之转贩日稀”。碑文中记卖瓜者的遭遇即一实例。换句话说,整个以苏州为中心的市场系统已陷于瘫痪了。所以整个事件象征了专制皇权和吴中商人阶层的一场生死搏斗。葛成之所以获得“四方商贾”的普遍爱戴,甚至“归而尸祝之,祠于江淮之间”,正是因为他的义举实质上为商人阶层争取了权利。而江南士大夫(包括现任地方官) 也因此在暗中对抗议事件多所调护。所以官方报告最后将抗议之事全推在“自食其力之良民”——织工——的身上,使朝廷无从追究。事实上,在成千上万的抗议民众中不可能完全没有中、小商人(如机户) 的参与的。
上述葛成的倡义事件最能说明晚明士商关系的密切:他们不但在社会背景方面混而难分,而且还在政治上同样受到以宦官为代表的专制皇权的高压,因此互相支援之事往往有之。 这是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可见16世纪社会变动的幅度之大。但士商联手与专制皇权相对抗毕竟不常见,更重要的则是他们长期在民间开拓社会和文化的空间。举凡建宗祠、修宗谱、建书院、设义塾、刊行图书之类的民间事业都是士与商共同为之,缺一不可。这也为儒学转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即以明末的商业书而言,其书名常以士商合称,如《士商类要》、《士商要览》皆其著例。这是因为士人出外考试也同样需要这一类的旅行指南。商业书的作者大都是早年受过儒家基本教育的商人,他们在提供必需的商业知识之外,往往还要加上一些道德的训诫。就我所见到的商业书而言,如《士商类要》卷二所载《贸易赋》、《经营说》、《醒迷论》,卷四《立身持己》、《养心穷理》、《孝顺父母》、《和睦家族》等篇,和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都是经商原理和道德训诫兼而有之。作者从商人的观点,用通俗的文字,对儒家伦理加以浅近的诠释,有些地方和明末的善书颇为相近。这些文字虽然没有学术思想上的价值,但却告诉我们儒家的若干核心观念是怎样通过商人而流传民间的。 这也是儒学转向的一个实例。
(五)儒学的宗教转向——以颜山农为例
最后,我想利用最近发现的资料,稍稍讨论一下泰州学派所代表的儒学转向。儒学自15、16世纪面对民间社会以后,它便进入自己的轨道,其发展与归趋往往不是事前所能逆料的。
儒学从政治取向转为社会取向,王阳明可以说是创始者。他的“良知说”和“满街都是圣人”说为后学开启了无限的诠释法门。但这一转向的完成则必须归功于王艮的泰州学派。王艮自初谒阳明,受到当头棒喝,从此便走上不为“政”而论“学”的一条路。他说:
社稷民人固莫非学,但以政为学最难。吾人莫若且做学而后入政。
在《答宗尚恩》(名部,号丸斋,王艮弟子) 的信中,他说得更为露骨:
古人谓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为学。此至当之论。吾丸斋且于师友处试之。若于人民社稷处试,恐不及救也。进修苟未精彻,便欲履此九三危地,某所未许。
王艮并非不关心政治,但他深知在君主专制的高峰时代,“入政”徒然陷自身于“危地”,绝不可能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所谓“且做学而后入政”不过是一句遁词而已。他论“道”、论“学”则以“百姓日用”为最后归宿,这就确立了泰州儒学走向民间社会的一条新路。所以明代儒学转向的政治背景在泰州一派的发展史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但以泰州学派而言,颜钧(山农,1504~1596) ,则是最具关键性的人物。同时代的王世贞(1526~1590) 撰《嘉隆江湖大侠》已说:“盖自东越(王阳明) 之变为泰州,犹未至大坏。而泰州之变为颜山农,则鱼馁肉烂,不可复支。”(《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五) 他对颜山农的聚徒讲学,甚至有“黄巾五斗之忧”。后来黄宗羲虽不同意王世贞的偏见,但也说:“泰州以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序》) 王、黄的评论,现代研究者常加引用。但是我们在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泰州门下的著作中并无法证实这样的看法。其原因即在颜山农的著作久已失传,我们看不到关于他的思想和社会活动的直接史料。最近《颜钧集》突然出现了,为泰州学派的研究开一新纪元。从全书来看,王世贞、黄宗羲把他看作是泰州学派史上划时代的人物确是有根据的,甚至“黄巾五斗之忧”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本文不能全面研究他的生平和思想。以下仅就颜山农的划时代性这一点上略作说明。
先师钱宾四先生曾指出:“守仁的良知学,本来可说是一种社会大众的哲学。但真落到社会大众手里,自然和在士大夫阶层中不同。单从这一点讲,我们却该认泰州一派为王学唯一的真传。” 这是一针见血的论断。朱熹、陆九渊的儒学传授还是以士大夫为直接的对象,对于社会大众不免尚隔一层,虽然他们的终极关怀是如何给社会大众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王阳明才在士大夫之外,同时也直接向社会大众说教。但阳明本人仍然是士大夫。王艮则出于小商人的背景。他的著籍弟子和私淑门人中有樵夫朱恕、陶业匠人韩贞、商人林讷等,还有七十人仅具姓名,不详里居事迹,看来至少不全是士大夫阶层中人。这才真是所谓社会大众。 阳明学在泰州一派的手上发生变化,是很自然的事。
现在我们要追问:王艮既已将儒学传给了社会大众,那么颜山农的特别重要性究在何处?是不是他比王艮更深入民间呢?还是他在儒家思想方面别有创辟,因此更适合社会大众的需要呢?对这两个问题,我们都不能无条件地给予肯定的答案。首先,我想我们不能过分强调颜山农的“平民性”。以交游而言,信仰和支持他的人似乎仍然以士大夫、各级官吏、普通儒生等为最多。这只要细看他遭难时,捐钱营救者的那一张颇长的名单,便很清楚了。 其次,以思想而言,他的信徒确认为他开创了新的境界。罗汝芳在为他鸣冤的《揭词》中说他“辞气不文,其与人札,三四读不可句。细味之,则的的能晰孔孟心旨,发先儒之所未发” 。以我所读到的颜山农文字而言,这段话的前半截是完全可信的,他的文字的确还没有达到“通顺”的程度。但后半截则要看我们用什么尺度去衡量他的思想。如果从阳明学的传统看,我们很难说他有什么创新的地方。事实上,他已脱出了理学的范围。但是如果从民间宗教的观点说,他在《道坛志规》中所宣布的“自立宇宙,不袭今古”则很能表达出他的开创精神。这正是他在泰州学派发展史上能够成为划时代人物的关键所在。
就我所见的颜山农有关思想的作品而言,他似乎不能算是思想家或哲学家,因为他既没有自觉地发展一套思想系统,也无意将自己的某些想法放进当时理学或心学传统之中。他的若干重要观念如“大成仁道”之类基本上来自王艮;他引用经典中片言只语如《大学》、《中庸》、《易经》之类,则不但望文生义,而且随意变换,比“六经注我”还要自由(《耕樵问答》篇可为明证) 。所以我认为研究颜山农,最好不要把他看作是《明儒学案》中的人物。严格地说,他的议论如果放进《明儒学案》是很不调和的。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他所体现的是一种真实的宗教生命,他的悟道和证道都是通过宗教的经验,而他所承担的主要也是一种救世的使命,那么他在泰州学派史上划时代的地位便十分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颜山农自出手眼的第一个讲学题目“急救心火”,详说见于《急救心火榜文》。这便十足地说明了他具有“救世”(salvation) 的宗教精神。儒学当然也一贯地讲“明道救世”,但其基本性格是属于俗世的(secular) ,即使有宗教的成分,也潜藏在后面。颜山农的“救世”则直接来自宗教的经验。他受王阳明良知说的启发而有“七日闭关”的悟道过程,从此形成了他的宗教性格。他在《七日闭关·开心孔昭》和《耕樵问答·七日闭关法》中详述其经验。原文太长,姑引他和门人谈话的一段为证。曾守约记他自叙说:
叙及平生事……乃知先生事亲至孝,学由天启,触阳明凝神融结之旨,而拳拳服膺。俄自觉坚如石、黑如墨、白气贯顶而纷然汗下,至七日恍若有得,其所谓七日来复者,非欤?《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盖天地之心以《复》而见,而先生学由自悟,学天启也,学由心也。先生之志,上通乎天;而先生之学,又不见于此《复》乎?是故《复》以自知,而阳明良知之学,先生得之矣。
如果仅止于此,我们还可以说,这是理学家“静坐”所同有的经验。下面引他在《自传》中的一节,则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他的宗教立场。他记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 甲辰秋和门人罗汝芳(近溪) 等在王艮祠堂中聚会的情形说:
秋尽放棹,携近溪同止安丰场心师祠。先聚祠,会半月,洞发心师传教自得《大学》、《中庸》之止至。上格冥苍,垂悬大中之象,在北辰圆圈内,甚显明,甚奇异。铎(按:颜山农因避万历帝之讳,改钧为铎,即以木铎自许之意)同近溪众友跪告曰:上苍果喜铎悟通大中学庸之肫灵,乞即大开云蔽,以快铎多斐之恳启。刚告毕,即从中开作大圈围,围外云霭不开,恰如皎月照应。铎等纵睹渝两时,庆乐无涯,叩头起谢师灵。是夜洞讲辚辚彻鸡鸣。出看天象,竟泯没矣。嗣是,翕徕百千余众,欣欣信达,大中学庸,合发显比,大半有志欲随铎成造。
这段文字有不甚通顺之处,也有误字,但大旨很清楚。从这一关于上天垂象的记述,我们可以认识到上一节中所谓“学由天启”、“上通乎天”的话并不是随便说说的。颜山农确深信“七日来复”已使他的心和“天心”相通也。现代受过所谓“科学洗礼”或倾向于实证思维的人自然很容易对这一段自述采取“不值一笑”的态度,甚至还可能认为这是颜山农和他的门徒们故意伪造的“神道设教”。但是如果我们对古今的宗教经验能保持一种同情的了解,则这一文件正是说明颜山农的宗教性格的重要证据。当时“天象”的真相究如何,今天已无从讨论,而且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颜山农率领门人跪告上苍“大开云蔽”,而居然好像立即得到了“天”的回应。这一“天象”的变化当然可能完全出于偶合,我们也只有置之不论。但问题在于在颜山农的意识中他是不是真诚地相信他的祈祷已使他的“心”和“天心”相通?在事隔四个半世纪的今天,无论我们说它是出于偶合、集体作伪或真诚信仰,都已没有证实或反证的可能。不过我相信颜山农当时不但自以为看到了某种天象的异变,并且更认定这是他祈祷的效应。我作此断定的理由有两个方面。
第一,这是宗教经验中最普遍的现象之一。
第二,颜山农在当时获得罗汝芳和其他许多人的真诚信仰并不是因为他在儒学思想上有特殊的造诣,而完全由于他的宗教人格所发挥的感化力量。黄宗羲引罗汝芳的证词云:
山农与余相处三十年,其心体精微,决难诈饰。不肖敢谓其学直接孔、孟,俟诸后圣,断断不惑。(《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序》)
另一位门人程学颜也说:
颜叨面受心领,退省足发,遂申申错综曰:大中学庸,庸中学大。天下人闻之,皆曰:此老好怪也。颜初及门,听之亦曰:此老真怪也。自燕南旋,忽(按:原书误作勿)迎此老,同舟联榻不下三旬日,朝夕听受,感悟隐思,渐次豁如,不觉自释其明辨,乃知此老竭力深造,自得贯彻。
罗、程两人都是因和他朝夕生活在一起才信仰他的教旨的。罗汝芳亲炙他的时间最久,故终生敬重他,且挺身而出,证明他“决难诈饰”。程学颜则最初也不信他所谓“大中学庸,庸中学大”的怪说,但一个月的“朝夕听受”却改疑为信。这都只有从颜山农的宗教人格方面才能得到解释。如果说颜山农在1544年忽然决定伙同罗汝芳和其他门人一起弄“神道设教”的把戏,以取得号召信徒的效果,那么整个泰州学派在此后几十年的发展便不可理解了,除非我们认定颜山农领导的泰州学派从开始便是一个江湖骗子或神棍集团。他的《自传》写于万历壬午(十年,1582年) ,相隔已三十八年,而他对当年天象的情况,记忆犹新,尤可见这一种经验在他心中所留下的深刻印象。此时罗汝芳尚存(罗卒于1588年) ,因此我们也不能说颜山农晚年编造天象的故事来神化自己,所以我断定1544年的天象是他生命史上一次重要的宗教经验,绝无可疑。
颜山农的宗教人格在他的教主心态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在《邱隅炉铸专造性命》中说:
孔子一生精神,独造大学中庸,晚创杏坛,聚斐居肆,肩承师任,陶冶己心人性。同修晬盎,自适乎左右逢原之身;各善立达,诱掖乎家齐国风仁天下……叨天降生阳明,引启良知,直指本心,洞开作人正路;继出淘东王心斋,自师孔仁,印正阳明之门,晚造大成之止。授传耕樵,肆力竭才,于七日闭关默识,洞透乎己心[人]性,若决沛江河,几不可遏,如左右逢原,惟变所适,三年五年,自得孔子师道之法程,翼后《大学》、《中庸》之绳脉……是故杏坛也,邱隅也,创始自孔子,继袭为山农,名虽不同,岁更二千余年,学教虽各神设,而镕心铸仁,实无两道两燮理也。
这是颜山农的道统系谱,自孔子以下只有二王(有时他也“孔颜”或“孔孟”并提) ,他自己则老实不客气地以儒门的现任教主自居。孔子、王阳明、王心斋在这个系谱中也都“教主化”了。这是颜山农的真信仰,所以他在《自传》中记他初见王心斋,得到了《大学》、《中庸》的“心印”之后,写信给心斋说:“千古正印,昨日东海传将来。” 从儒学史说,他的道统系谱可谓荒谬绝伦,一无是处。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他并不是站在理学传统之内发言,而是企图化儒学为民间宗教,那么这一系谱便是可以理解的了。他在《耕樵问答·七日闭关法》中又说:
人生出世,各各同具有亦孔之昭,潜伏为腔寰之灵,尽被知识见闻偃埋,名利声色侵沸,胜若溺水益深、入火益热矣。所以群类中突出一个人豪住世,自负有极样高大志气者,并遭拂逆危挫,人皆不堪其忧苦累累。然日夜自能寻思,何日得一出头大路,竟步长往以遂志?
这明明是“夫子自道”,大有“天生德于予”的意味,其救世教主的自信力也表露无遗。
我读他的全集,包括不少诗、歌,差不多全讲的是他个人“证道”的宗教经验。他的一切文字都必须从宗教层面去了解,才能显出他的特色。若以哲学或文学的眼光读之,则会使人感到深深的失望。所以我相信他生前能感动许多第一流的学人,全靠这一股深沉的宗教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重视他在八十六岁时(万历十七年,1589年) 所写的《履历》一文。此文或包括九十岁左右的增补,故是晚年一篇最重要的精神自传。兹引其中一小段以说明他的宗教历程:
我朝天道中兴,阳明唤醒良知,开人心目,功同东日之启明;继承心斋,洞发乐学,丕振大成,几将聚斐为显丽。不期二老相继不寿,不克显比天下。樵当际会,有缘先立徐师波石之门,随任住京畿三年,叨获造就三教活几,继入淘东师祖王心斋坛上,规受三月,乐学大成正造,快遂自心,仁神阃奥,直任夫子至德要道,以仁天下人心,曰:千古正印,昨日东海传将来;四方公凭,今朝西江发出去。如(无)何以别心斋,心斋在床,鼓跃曰:今日斯道得人如此,天下庆幸,万世庆幸。樵农快志,毕力遂行,四十余年,几将通乎君相……叨享天年八十有六,将渝颐百之外,皆可自致自滔滔也。此之谓自绪生平学道履历,即今营图结果,虽近溪仙游,农志尚能独致。敢曰:不俦宣尼忍自已。复曰:不续杏坛肯甘死也。
这段晚年回忆他继承道统的经历,特别添上王艮在病榻上亲将“心印”传授给他的故事,尤值得注意。此时罗汝芳已先逝,只剩下他一个人在独承传道、弘道的重任。他的信念依然坚定不移,但是语气之中却不免有苍凉的意味了。儒学在他的手上已转化为宗教,这是毫无可疑的。
至于他的讲学活动,那便更近于宗教性的传道了。他讲学最喜人多,少则数百,多至数千,《自传》中详记其事。从《告天下同志书》和《道坛志规》两篇文字看,他其实是借“讲学”以从事于“传教”的工作。在他所处的时代,他自然未必能清楚地划分二者之间的界线。但从现代的眼光看,他的基本旨趣在于化儒学为宗教,则是无法掩饰的。 在此我们不能不继续追问:颜山农“传教”的对象究竟是谁?就我所见的资料说,他当然也欢迎一般平民来参加讲会,但是他首先想吸引的还是中、上层的士人。他曾受辅相徐阶之邀,在北京灵济宫向三百五十名入觐官员会讲三日,又与七百名会试举人“洞讲三日”,这两件事都是他生平的得意之笔。其余大规模的讲会也往往是由地方官安排的,并且听众也以乡试生员或南太学的监生为主体(均见《自传》) 。不但如此,他还对江西巡抚何迁(吉阳) 说过:“生平游江湖,不得官舟,广聚英材讲学为恨耳。” 这句话清楚地表示出士人是他所最重视的“传教”的对象。但这只是就“传教”的程序言,才是如此。至于他的“救世”的对象则自然是社会上各阶层、各行业的人。他显然认为“士”是最能影响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为了“传教”于天下,他每先和“多士商兑共事”,吸引他们为“会友”,然后由他们来“引掖四方”,则天下岂有不“观化”、千古岂有不“式程”者乎?(见《道坛志规》) 换句话说,他是要广泛地接引士人,把他们变成他所需要的“传教士”。这不但流露出他的儒学背景,而且也是社会现实使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虽然号称“四民之首”,但并不构成一个固定的社会阶段,他们在科举制度之下,或浮或沉。在本篇开始时,我已引了16世纪人有关“士之成功也十之一”的说法。这就是说,上浮者才十分之一,下沉者竟高达十分之九了。但是,尽管如此,社会上普通的人仍然对“士”保持着一种敬意,认为他们“读书明理”,可以为世人指点信仰上的“迷津”。晚明儒学转向了,由“上行”的“得君行道”改为“下行”的“化民成俗”。因此社会上一般人对“士”的期待也相应而提高了。颜山农化儒学为宗教而首先重视“士”的阶层,其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便在于此。
但是我们要真正了解颜山农化儒学为宗教的历史意义,便不能不引同时代的不同型的儒学转向作一简明的对照。晚明儒学转向是一普遍的文化现象,但有的走得远,有的走得近。走得近的可以东林学派的钱启新、高攀龙等人在无锡组织的同善会为代表。从高攀龙集中保存的三篇《同善会讲语》来看,这确是儒家普及化的社会讲学,其内容是善书水准的通俗儒学(包括天人感应说) ,其语言则是纯粹口语,即今天所谓“白话”。但是同善会绝无宗教气味,而只能归类为地方性的道德兼慈善团体。 走得最远的则是林兆恩(1517~1598) 在福建莆田所创建的三一教。林兆恩虽比颜山农小十三岁,但是他们的活动期间几乎完全重叠,正可视之为处于儒学转向大潮流下同时代的人。更重要的是林兆恩的“心法”和“三教合一”说都源于王阳明的心学,而且他与阳明的弟子罗洪先和颜山农的弟子何心隐也颇有交往。但他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 第四次乡试落第之后,终于在嘉靖三十年正式创立了三一教。据他自己的解释,三一教的归宿处仍是儒,这是一种打通出世间与世间的立场。阳明后学持此立场者不计其数,王畿(龙溪) 尤其著者。故李贽称他为“三教宗师”。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断定林兆恩所走的还是化儒学为宗教的一条路。只是由于儒家毕竟偏重于世间法,他才不得不把专讲出世间法的释、道两教搬进来,因为不如此则宗教的性格终不够完整。在三一教草创期的十余年间,林兆恩交往和接引的对象也是中、上层的士人。他甚至还以“习举子业”为号召教徒的手段。在这一立教的程序上,他和颜山农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万历末期(约在1563~1566年之间) 基础确立之后,他便正式以教主的姿态出现了,而三一教也完全向民间各阶层的人开放了。
颜山农恰好处于同善会和三一教之间。他已超过了儒家的民间讲学的阶段,走上了化儒学为宗教的道路。也许由于他的背景毕竟是王阳明和王心斋的儒家传统,虽然他也畅谈三教,却认为孔子的圣学发展到最高阶段即是以“神道设教”,佛教、仙教终不及“尼父之传”是“坦平之直道” 。所以,他主观上虽已具备了宗教的基本要素,客观地说,他化儒学为宗教的工作并未完成,至少在三一教的对比之下是如此。但是他的宗教取向则是毫无可疑的,而且在宗教史上也自成一型态。如果用韦伯(Max Weber) 所划分的宗教类型,我想颜山农可以归于“先知”(prophet) 和“伦理教师”(teacher of ethics) 的混合型;他的宗教组织则是由俗世门徒构成的“同志会”(这是用他自己的名称,韦伯则称之为“congregation of laymen”) 。
结语
本篇的主旨在讨论明清社会变动与儒学转向的关系。在社会变动的范畴之中,我仅仅强调了士商合流和专制政治两个方面,而且对前一方面所论稍详,对后一方则仅略举例以示一二。但这是限于史料和我目前的研究重点而然,并不表示本篇所论已足以概括当时社会变动的主要内容。我所用的“社会变动”也是一个富于弹性的概念。和今天绝大多数的史学研究者一样,我并不接受所谓“下层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种二分法。因此社会变动可以来自任何方面,包括社会心理的变化。16世纪以来的社会变动确为儒学的转向提供了契机。但转向一经开始,儒学便通过各种形态的发展而参与社会变动,如上面提到的颜山农的传道活动、东林的社会讲学、林兆恩的三一教等都成了当时社会变动的一部分。所以这里并不涵蕴着儒学仅仅是被动地适应社会变动的意思。“弃儒就贾”在开始时自然一部分是由于商业发展本身的吸引力,但是大批儒生参加商人的行列之后,儒家的观念和价值也或多或少对经商方式发生了某些规定的作用。
儒学转向包括了宗教化的途径,而与释、道两教合流,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视的现象。从宗教史的角度看,这一现象恰好可以说明16世纪的社会变动并不限于经济和政治的领域,而必须扩大到社会心理的方面。但是这已佚出本篇范围之外,此处只能略缀数语以明儒学的宗教化的历史背景而已。16世纪可以说是中国宗教史上一个最有活力的时代。除了上面已提到的王阳明一派的三教合一说之外,佛教的重振也是万历一朝的大事。以民间宗教而言,罗教、黄天道、弘阳教、大乘教等都兴起于15世纪末以后。下至17世纪初年耶稣会教士东来,也取得了不少士大夫的崇信。明末清初又有徽商程智(云庄,1602~1651) 创大成教,其教旨也是三教合一,或从林兆恩那里转手而来。程智在江浙一带信徒很多,所以引起了黄宗羲的注意。 宗教活力在这一个多世纪中如此旺盛,而且遍及于社会各阶层,这便不能不使我们想到这一凸出的宗教现象也许是社会心理长期激荡不安的一种表现。换句话说,晚明以来中国人似乎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信仰或精神的危机。由于这个大问题史学家还没有开始认真地研究,我的话暂时只能到此为止。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普遍的宗教现象,主要是想说明颜山农化儒学为宗教的倾向不能仅从儒学内部的发展去求了解。即以外缘影响而言,本篇所讨论的士商混合和政治背景也远不足以解释儒学为什么会和释、道二教合流,走上宗教化的道路。 我们只有把宗教变动也当作社会变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然后将颜山农的宗教化运动放在这一更广阔的视野之中,晚明儒学转向的历史意义才能获得比较完整的理解。
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
一、 历史背景——道光时代(1821~1850)的学术界
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 ,他的成学则在道光时代。我们必须对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状况有一个概括的认识,然后才能了解曾国藩的学术渊源之所自。近人王国维说:
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学者尚承乾、嘉之风,然其时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忧之而不知所出,乃或托于先秦、两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然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如龚璱人、魏默深之俦,其学在道、咸后虽不逮国初、乾嘉二派之盛,然为此二派之所不能摄,其逸而出此者,亦时势使之然也。
王国维论道光、咸丰以降的学术新路向,因限于寿序的文体,仅举龚自珍、魏源的今文经学为代表,但他在嘉庆与道光之间截然划一学术史上的分界,则是十分确切的。
所谓道光学术之“新”,本相对于乾嘉而言。乾嘉的经学考证以“汉学”为标榜,当时几乎有“定于一尊”的趋势。袁枚(1716~1798) 说:“近今之士,竞争汉儒之学,排击宋儒,几乎南北皆是矣。豪健者尤争先焉。” 这是亲见汉学盛世的人的证词。下及嘉庆时期,情况依然未变。满清宗室昭梿(1780~1833) 在嘉庆二十年(1815) 左右写的《啸亭杂录》中记载:
自于(敏中)、和(珅)当权后,朝士习为奔竞,弃置正道,黠者诟詈正人,以文己过,迂者株守考订,訾议宋儒,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余尝购求薛文清(瑄)《读书记》(按:“记”当作“录”)及胡居仁《居业录》诸书于书坊中,贾者云:“近二十余年,坊中久不贮此种书,恐其无人市易,徒伤赀本耳!”伤哉是言,主文衡者可不省欤?(卷十“书贾语”条)
嘉庆时北京书店竟买不到理学的书,如果不是看到这条笔记,我们是很难想象的。
汉学考证的独霸之局,进入道光时期,便开始瓦解了。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在消极方面,乾隆时代的最后几位大师都在嘉庆年间死去了,如钱大昕死在嘉庆九年(1804) 、程瑶田死在嘉庆十九年(1814) 、段玉裁死在嘉庆二十年(1815) 。道光初年,虽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尚存,阮元(1764~1849) 更是经学考证的有力护法,但汉学盛极而衰,它的霸权毕竟不能维持了。最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莫过于方东树在道光六年(1826) 写成《汉学商兑》一书(刊于道光十一年) 。方氏是姚鼐的四大弟子之一。道光初年,他正在广州阮元的幕府中。《汉学商兑》完稿后,他即献之阮元求教。这是一部最有系统的反汉学的著作,作者深入汉学堂奥,入室操戈,所以刊行后引起重大的反响。清末李慈铭颇为汉学辩护,但他也不能不承认方氏“颇究心经注,以淹洽称,而好与汉学为难。《汉学商兑》一书,多所弹驳,言伪而辩,一时汉学之焰,几为之熄” 。“汉学之焰,几为之熄”自然是一句夸大之词,但《汉学商兑》确是正式向汉学霸权挑战的一个信号,这就表示道光以后中国学术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在积极的一方面,新的时势对学术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则不是经学考证所能满足的。乾隆一朝是清代所谓“太平盛世”。尽管乾隆晚期各种社会和政治的危机已开始出现(如“回乱”、“川楚教匪”之类) ,但表面上还能维持着一种“太平”的假象。汉学考证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在乾隆中叶不但足以点缀太平,而且也为整理学术传统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当时许多第一流的人才愿意献身于此,也是因为他们在其中获得了求知的乐趣、发挥了创造的精神。
但道光以后,内忧外患并发,深刻的危机感使许多读书人不复能从容治学,走经典考证的老路了。这时的知识界可以说是普遍地要求改变现状。而且这种要求早在嘉庆一朝便已见诸文字。例如,关于士大夫的风俗颓坏,洪亮吉(1746~1809) 、管同(1780~1831) 、沈垚(1798~1840) 诸人先后都有很严厉的指责。又如对于新人才的期待,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更是万口传诵。曾国藩的《原才》之所以成为名篇,正是因为他用简练有力的古文把“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的意思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如果我们不认清历史背景,便不可能真正掌握曾氏的思想渊源。
道光以下的学术精神从古典研究转为经世致用,大体上说,有两个比较显著的趋向:第一是理学的重新抬头,第二是经世之学的兴起。这两个趋向都与曾国藩的学术成就有密切的关系。就第一层言,方东树向“汉学”挑战同时即是为“宋学”作平反,并由此而展开了一场长期的汉宋之争(也可称之为考证与义理之争) 。但是在考证的成绩大显之后,提倡宋学的人也不能完全否定汉学的功用。所以争议的焦点最后集中在如何融汇汉宋。陈澧(1810~1882) 晚年的《东塾读书记》是这一大问题的一个总结。曾国藩在这一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他曾旗帜鲜明地宣称:
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
在那个时代,这种斩截的态度对于理学是发生了起信的作用的。关于这一点,下面将有进一步的讨论。
就第二层说,经世之学的内容相当复杂,举凡道、咸以下的新兴学术如礼制、史学、掌故、时务(如漕运、盐法、河工、兵饷等) 、边疆与域外史地等无不与“经世”有关。即使是今文经学,名为解经,其实也是要为变法、改制提供经典的根据,其基本精神即是所谓“通经致用”。我们不妨说,道光以下的理学与经世之学是一事之两面,统一在实践这个观念之下;所不同者,理学注重个人的道德实践,经世之学则强调整体的社会、政治实践。因此在精神上,两者与乾嘉经学之为学院式的研究恰恰相反。
道光六年(1826) ,魏源为贺长龄辑成《皇朝经世文编》,这是晚清经世思想出现的标志。 《皇朝经世文编》收录顾炎武《日知录》中有关经世实务的文字甚多,这也反映了道光时学者的一种共识。李兆洛(1769~1841) 在道光初特别指出,《日知录》论时务八卷为全书精华所在。 同时黄汝成(1799~1837) 撰《日知录集释》,也说顾氏“负经世之志,著资治之书” 。总之,道光以后学者推重顾炎武主要在他的“经世”之学,与乾、嘉时奉他为经学考证的开山大师大不相同。
曾国藩在北京翰林院进修时期便受到经世学风的感染。根据他的《日记》,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九收到家中寄来的一部《皇朝经世文编》,二十日他便开始阅读。这部书大概他随时携在身边,因为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在《日记》中也记载:“阅《经世文编》十余首。”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唐鉴要他治义理之学,但他仍念念不忘地问道:“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咸丰九年他写成著名的《圣哲画像记》,其中清代学者即首举顾炎武。他说:
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
可知他所景仰的不是乾、嘉时代共奉为考证始祖的顾炎武,而是道光以下群推为经世儒宗的顾炎武。
二、 曾国藩的成学过程
曾国藩的出身并不是所谓“诗礼世家”,他只是湖南湘乡一个半耕半读之家的子弟。他的父亲在四十三岁才考上县学的生员(秀才) 。这样的身世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的环境使他在中年以前接触不到当时学术的主流,因此他注定了不能走专业研究的道路。
三、 曾国藩的“读书之道”
曾国藩《日记》咸丰九年五月十二日:
读书之道,杜元凯称,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若见闻太寡,蕴蓄太浅,譬犹一勺之水,断无转相灌注、润泽丰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
这是他一生所悬的读书理想,其义亦发自朱子。(《朱子语类》卷十《读书法下》云:“读书要自家道理浃洽透彻。杜元凯云:‘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 同年四月二十一日他有一封《谕纪泽》的长函,“示以读书之法,宜求博观约取”(见同日的《日记》) 。所以他的理想也可以用“博观约取”四字来概括。这四个字本是老生常谈,但由曾国藩口中说出则特具一种亲切而严肃的意味,因为他一生都在努力实践这个理想。更重要的,他的重点是放在“约取”上面,其目的是要造成一种“诗书宽大之气”(黄宗羲语) 的士大夫人格。现代社会学中虽有“价值内化”这个名词勉强可与“约取”相比附,但在精神境界上相去甚远。曾国藩晚年有一段自我省察的话可以进一步澄清有关“读书之道”的含义:
念余生平虽颇好看书,总不免好名好胜之见参预其间。是以无《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无杜元凯“优柔餍饫”一段之趣,故到老而无一书可恃,无一事有成。今虽暮齿衰迈,当从“敬静纯淡”四字上痛下功夫,纵不能如孟子、元凯之所云,但养得胸中一种恬静书味,亦稍是自足矣。
这里他用《孟子·离娄下》“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来补充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的话,更可见他认为读书的最高境界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料,以转化个人的人格。用《论语》的话说,这便是所谓“为己”之学。他曾将清代学者分为“为人”的和“为己”的两型,而以后者为更可贵。他说:
默念本朝博学之家,信多闳儒硕士,而其中为人者多,为己者少。如顾(炎武)、阎(若璩)并称,顾则为己,阎则不免人之见者存。江(永)、戴(震)并称,江则为己,戴则不免人之见者存。段(玉裁)、王(念孙、引之父子)并称,王则为己,段则不免人之见者存。方(苞)、刘(大櫆)、姚(鼐)并称,方、姚为己,刘则不免人之见者存。……学者用力,固宜于幽独之中,先将为己为人之界分别明白,然后审端致功。种桃得桃,种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叶发生、能自鬯茂者也。
他划分清儒的“人”、“己”之界是否一一恰如其分,自可争论,但“为己”是他的中心价值,而且和“自得”、“约取”义旨一贯,这似乎是可以断言的。这当然只是一个“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理想境界,恐怕没有人能彻底实践它。曾国藩便自承失败,他也未能全免于“好名好胜之心”的干扰。一涉“好名好胜”,读书便是“为人”了。但由于曾国藩时时悬此理想以自勉,他对于“读书之道”确有亲切的体会和通达的见解。从清末到民初,他的《家书》、《家训》流行甚广,他的读书观因此影响了好几代的青年读者。
这里我要特别指出一点,曾国藩的读书观是发展的,并未停止在最初的成学阶段。上面我们已讨论过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这一时期在他的学术生命史上的重大意义。他的学问大体虽已在此时定型,但通过实践,他在已成的规模之内仍随时有所调整,而且有些调整是相当基本性的。
曾国藩是一个有创造力和判断力的人。他一方面虚心受师友之教,另一方面却不轻易屈己从人,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前引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唐鉴的一番话对他诚有“昭然若发蒙”之功,但他并不墨守唐氏之说,他接受了唐氏的程、朱之学,承认义理是学问的主宰。但“义理”在他那里主要落实在两个方面:一是修身律己,即以“主敬”、“格物”、“诚意”等德目来检查自己日常行为中的动机;一是指读书时要集中力量抓住书中(无论是经、史、子、集) 的大道理,并且以书中道理和自己的切身经验互相印证。基本上这是从朱子“读书法”中提炼出来的。总之,他重视的是实践,而不是理论。与唐鉴不同,他并未以理学家自居,更未以承继道统自任。对于唐氏所划分的“传道”、“翼道”、“守道”等名目,他则置于不议不论之列。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书学案小识后》之结尾处还特别强调“无以闻道自标”。这绝不是一句普通的谦词。《日记》咸丰九年二月初八日载:
夜与子序(按:吴嘉宾)鬯叙,言读书之道,朝闻道而夕死,殊不易易。闻道者必真知而笃信之。吾辈自己先不能自信,心中已无把握,焉能闻道?
他肯这样说老实话,这就证明他无意盗“理学家”之名以欺世。咸丰十年十二月十二日,他指出一个“勤”字、一个“谦”字,并在《日记》中说:“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倘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但这是人人都能“闻”之“道”,不是一般理学家所说的那个“道体”了。
曾国藩的读书观点前后变化得最大的是在考据之学方面,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他在《致诸位老弟》的信中说:
盖自两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
此时他正在唐鉴的思想笼罩之下,所以这里所反映的也完全是唐氏关于义理、词章、考据的评价。依照这个看法,曾国藩应该终身不会涉考据学的樊篱。然而不然,《年谱》道光二十六年载:
夏秋之交,公病肺热,僦居城南报国寺,闭门静坐,携金坛段氏所注《说文解字》一书,以供披览。汉阳刘公传莹,精考据之学,好为深沉之思,与公尤莫逆,每从于寺舍,兀坐相对竟日。刘公谓近代儒者崇尚考据,敝精神费日力而无当于身心,恒以详说反约之旨交相勖勉。
据此,则至迟在道光二十六年曾氏已开始读考据的著作,这大概是受了刘传莹的影响。虽然他们都视考据为第二义的学问,但他们显然也同样承认,生在乾嘉以后读经书的人必须通过考据的关口。此后他在《日记》中不断留下读清代考据家著作的记录。举其要者如顾炎武《日知录》(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王引之《经义述闻》、 《经传释词》(同年十二月十六、十七日) 、王念孙《读书杂志》(咸丰九年正月十六日) 、《戴东原集》(同年正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赵翼《陔余丛考》(同年三月二十八日) 、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同治元年五月二十日) 、段玉裁《六书音韵表》(同治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戴震《绪言》、钱大昕《声类》(同年同月二十八日) 、《王念孙文集》(同年二月初四) 、《钱大昕文集》、《十驾斋养新录》(同年五月初一) 、江藩《汉学师承记》(同年同月二十九日) 。他对高邮王氏父子的训诂尤为倾服,故《圣哲画像记》三十二人中以王氏为殿。 但最能代表他后期对于考据学的看法的则是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谕纪泽》一信,此信结语说:
学问之途,自汉至唐,风气略同;自宋至明,风气略同;国朝又自成一种风气。其尤著者,不过顾(炎武)、阎百诗、戴东原、江慎修、钱辛楣、秦味经、段懋堂、王怀祖数人,而风会所扇,群彦云兴。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
这才是他学问成熟以后的见解,与早年“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的态度,相去何止万里。他不但在中年以后勤读清代考据家著作,而且论学方式也转为注重“证据”。姑举两例以说明之。咸丰八年十一月初四日他读友人吴嘉宾的《诗经说》,评曰:
夜,阅子序《诗经说》,学有根柢,其用意往往得古人深处,特证据太少,恐不足以大鸣于世耳。
这一评论的观点基本上取自考据之学,若在道光二十三年前后,他绝不会如此说。第二例是他晚年的一首五古诗《题俞荫甫〈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后》。在“旁证通百泉,清辞皎初雪”句下,他自注曰:
王氏(按:念孙、引之父子)立训,必有确据。每讥昔人望文生训,或一字而引数十证。其反复证明乃通者,必曲畅其说,使人易晓。
此时他已完全了解“立训必有确据”及“一字而引数十证”这种考据式的重要性了。他不但评论时人的著作时遵用考据的标准,而且晚年研究礼经也以考据自律。同治五年九月的两条《日记》可以为证:
阅《仪礼·士丧礼》,以张稷若(尔岐,1612~1677)句读、张皋文(惠言,1761~1802)图为主,而参看徐继庵(乾学,1631~1694)、江慎修(永)、秦味经(蕙田)诸书。(二十一日)
阅《读礼通考》,《疾病》、《正终》二卷及《始死》、《开元》、《政和》、《二礼》、《书仪》、《家礼》等,考证异同。(二十九日)
甚至他自己也在进行某种程度的考据工作了。
以上追溯曾国藩对考据之学的态度的先后变化,并不是要证明他中岁以后已转为考据学家,而是要借此说明他的“读书之道”与年俱进,一直在扩大发展之中。而他之所以能够发展,则又由于他具有一种开放的求知精神。这一精神尤其表现在“转益多师”上面,即从四面八方吸收师友的长处。上面已指出,他的“义理之学”得力于邵懿辰、唐鉴、倭仁,“考据之学”则启发于刘传莹。他的“词章之学”最初则颇受何绍基(子贞) 的激励。他曾在家书中说何氏“各体诗好……远出时手之上,(而) 能卓然成家。近日京城诗家颇少,故余亦欲多作几首” 。他的古文私淑姚鼐桐城派,但也渊源于朋友间互相切磋。从《欧阳生文集序》与早年《日记》参伍以求,吴嘉宾(子序) 、孙鼎臣(芝房) 两人的影响似乎最大。但更可贵的是他在“博观”中不忘“约取”,终于完成了自己特有的“读书之道”。
四、结语
曾国藩在《日记》和《家书》中谈学问和读书,都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而来的。《日记》的作用主要在自警,《家书》的对象自然是他家中的子弟,所以此中并无门面语;他所说的或者是已实践的,或者是仍在实践之中但尚未能甚至永远无法完全做到的。就这一方面说,他的《日记》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从不间断的实践。他大致有一个指导性的读书原则,即生书必须快读以求广博,旧书必须熟读以求约取。因此,在《日记》中我们看到种种不同名称的读书方式,如“温”是温习已读的旧书,“圈”是精读而加以圈点,“读”是认真地研读,“阅”或“看”则多半是浏览生书或非经典性的文字。所以“看”可以包括小说,如《绿野仙踪》、《儒林外史》、《水浒传》、《红楼梦》等。对于他最欣赏的诗赋之类,他有时还“朗吟”或“诵”。一般地说,他在较为闲暇的时候,每天“温”故“阅”新,交互进行;但在忙乱的日子里,如打仗或途中,则以“温”旧书为常。总之,他差不多真正做到了“手不释卷” 的地步,如同治五年四月十九日他在剿捻途中记道:
前所阅《选举考》十一、十二卷不甚仔细,昨日重看三十余叶,本日重看二十余叶,车中摇簸,殊费目力耳。
又如同治七年底,他从金陵路程入京,途中四十多天他每日在“温”《左传》或“阅”《国语》、《战国策》。这样的实践精神确不多见。
从学问的整体出发,他读书自是以成就人格为最高的理想。然而这并不是说他完全不讲求实用。他为了“经世”而读书的情况在《日记》中也随处可见。姑举一例,以概其余。《日记》同治六年十月初五日:
余阅《瀛寰志略》四十叶,盖久不看此书,近阅通商房公牍,各外洋国名茫不能知,故复一涉览耳。
这一年他虽留任两江总督,但又加大学士衔,总理衙门要他预筹与外国换条约的事宜。所以从十月初五到十一月初八,他读了两遍《瀛寰志略》。
曾国藩治“义理之学”而无意入《道学传》,治“考据之学”而无意入《儒林传》,治“词章之学”也无意入《文苑传》。但当时及后世的公论,他的诗文在晚清文学史上都应该占一个位置。
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一)知识人与“道”
知识人在古代中国叫做“士”,而“士”的出现则是和“道”的观念分不开的,所以孔子说:“士志于道。”(《论语·里仁》) 但是“士”和“道”两个名词在孔子以前早已存在,其含义也颇有不同。让我们先简单地谈一谈孔子以前的情况。
商、周文献中常见“多士”、“庶士”、“卿士”等称号,这一类的“士”大概是当时“知书识礼”的贵族。商代卜辞中所见的“卜人”也许便是“士”的一种。《说文解字》和《白虎通》都说“士,事也”。因此今天不少学者都相信,商、周文献中的“士”,是指在政府中担任各种“职事”的人。周代的教育以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为主,受过“六艺”训练的人也称作“术士”或“儒”;他们可以根据自己擅长的技艺而出任不同的“职事”。例如孔子曾为“委吏”,是管理仓库、核查出入数字的职事。这当然必须学过六艺中的“数”。孔子自己又说过:“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论语·子罕》) 可见他也学过“御”和“射”。至于“礼”和“乐”,则更是孔子研究得最深的两门艺业。“礼”和“乐”在古代贵族社会中的用途最广,学了这两种知识技能之后,更可以有许多“事”可做,如各种“相礼”和“乐师”。所以,《说文》以“事”来解释“士”确是有根据的。
在孔子以前,“道”的观念大体上是指“天道”,即以“天道”的变化来说明人事的吉凶祸福。关于这一点,清代钱大昕已有很扼要的考证。他说:
古书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祸福而言。《古文尚书》: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天道福善而祸淫。《易传》:天道亏盈而益谦。《春秋传》:天道多在西北。天道远,人道迩。灶焉知天道!天道不謟。《国语》:天道赏善而罚淫。我非瞽史,焉知天道?《老子》: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皆论吉凶之数。(《十驾斋养新录》卷三《天道》)
春秋以前还没有《论语》、《老子》中所说的抽象之“道”;“道”字单独使用,其本义只是人走的“路”。故《说文》云:“道,所行道也。”
总之,古代的“士”是政府各部门中掌“事”的官员,所以顾炎武说:“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日知录》卷七《士何事》) 另一方面,古代也没有发展出一种普遍而抽象的“道”的观念。春秋以前的所谓“天道”则是具体的,主管着人间的吉凶祸福。这种“天道”还没完全脱离原始宗教(primitive religion) 的阶段。在原始宗教中,只有少数有特殊能力的人,可以成为天人或神人之间的媒介,如商代的卜人,周代的巫、瞽或史。但是卜人、巫、瞽或史只是“士”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士”则和“天道”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单襄公答鲁成公之问,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国语·周语下》) 据韦昭的注解,瞽是乐太师,掌音乐,听军声以察凶吉;史是太史,掌天时。这两种人的职事都是“知天道”的。
由此可知,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是指一种新出现的历史情况,和春秋以前的传统截然不同。这一新情况的出现,说明“士”和“道”两个观念,在春秋时代都发生了基本的变化。
(二)哲学突破与内向超越
清代章学诚(1738~1801) 在《文史通义·原道中》说过:“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用现代的话说,他的意思是:在孔子以前,政治和思想是合一的,学者还没有一种超越的观点(“心无越思”) ,所以他们只能从自己的职位上考虑具体的问题(“器”) ,而不能对政治社会秩序的本质(“道”) 有整体的理解。但在孔子以后,政治和思想分家了,学者的聪明才智不再受到限制,因此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禀性(endowed nature) 去发挥独特的见解,并且都自以为看到了“道”的全貌。章学诚最后说:“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这是一个很有现代眼光的深刻观察,但是其根据则在《庄子·天下》篇。《天下》篇说: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天下》篇的作者指出古代统一性的“道”,在战国时代已完全破裂了,因此才有诸子百家的兴起;他们都各自得到了“道”的一部分。这确是中国“道”的历史一大变化,其他古代思想家也有同样的观察。荀子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又指出诸子各有所“蔽”,所见到的“皆道之一隅”(《荀子·解蔽篇》) 。《淮南子·俶真训》则说:“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裂) 道而议,分徒而讼。”这都可以证明章学诚的论点是正确的;诸子都纷纷言“道”,并且都要“以其‘道’易天下”,正是因为他们都已有了超越的观点,成为自由的知识人了。
“道”的观念的重大变化,也发生在孔子的时代。首先是原始的“天道”信仰发生了动摇。
……
世间和超世间仍是不即不离的。由此可知,中国古代的“超越的突破”,事实上,决定了此下两千多年的思想传统,也决定了中国知识人的基本性格。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不但适用于先秦时代的儒家知识人,而且也同样适用于后世各派的知识人。中国的“道”从一开始便具有特色,我们可以称这种特色为“内向的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 。中国知识人大体上带有“内向超越”的色彩。
(三)内向超越与“改变世界”
马克思(Marx) 曾说:“哲学家从来只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真正的关键是改变它。”(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in various ways;the point,however,is to change it.) 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西方知识人的两大类型。“解释世界”的哲学家是西方古代和中古的知识人;“改变世界”的则是西方近代和现代的知识人。古希腊“哲学的突破”是外在的超越(external transcendence) ,超世间而高于世间,但又外在于世间。因此哲学家的主要兴趣贯注在永恒不变的超越本体或真理世界,他们以思辨理性(speculative or theoretical reason) 对超越世间进行静观冥想(contemplation) ,而不大肯注意流变扰攘的世间生活。自苏格拉底因为卷入城邦的政治生活而被判处死刑以后,古希腊的哲学家更不肯参加政治生活了。 柏拉图以来,西方文化史上出现了“静观的人生”(vita contemplativa) 和“行动的人生”(vita activa) 的划分。哲学家“解释世界”便是“静观”的结果。中古的经院哲学家(schoolmen) 仍然继续着“静观的人生”。另一方面,西方中古基督教教会(church) 则承担了“改变世界”的任务,因为基督教是根据上帝的旨意而“救世”的。欧洲中古时代的教会对所谓“蛮族”(barbarians) 进行教化,对君主的权力加以限制,同时又发展了学术和教育。这些都属于“改变世界”的工作,也就是“行动的人生”。西方近代和现代的知识人是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 以后才大批出现的。这是西方文化“世俗化”(secularization) 的结果。18世纪以后的西方知识人才转而重视“行动”与“实践”(practice) ;西方近代史上的革命,都有知识人的参与和领导。
与西方的情况相对照,我们便能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知识人的特征,这些特征大都和“道”的内向超越性有关。第一,中国知识人自始便以超世间的精神来过问世间的事。换句话说,他们要用“道”来“改变世界”。
(四)修身正心与“道”的保证
内向超越给中国知识人带来另一个显著特征,即重视个人的精神修养。这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或多数的中国知识人在精神修养方面具有真实的成就,更不是说中国知识人的平均精神水平,高于其他民族的知识人。我们所注意的是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对于知识人特别提出精神修养的要求?而且这个要求至少从孔子起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失?
我们首先要指出的是:自中国古代“超越的突破”以后,“修身”或“修己”是儒、墨、道各家所共同强调的一个观念。
……
上面已指出,中国古代的“突破”起于“礼坏乐崩”。“突破”之后,各派思想家都对“礼”的传统加以改造,其结果是使原来讲身体修饰的“礼”,变成了精神的修养。上引孔子、墨子、老子三家的话,显然都是指精神的状态——“敬”、“义”、“德”。不但如此,孔子的“修己以敬”和墨子的“修其身”,又同是以“君子”为对象。“君子”在孔、墨时代则是以“士”为主体。这不是说“士”以外的人可以完全不需要修养。荀子便说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安正。”(《荀子·君道篇》) 《大学》也说:“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第一章) 但是先秦诸家论精神修养,特别是以知识人为对象,则是不成问题的。
……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内向超越”的具体方式。“突破”以前的“天道”以吉凶祸福为主,这是因为古人相信天上有“帝”或“上帝”在那里主宰着人的命运。“突破”以后,“道”的重心逐渐向“人”的方面移动,但“天”的源头并没有因此而被切断。董仲舒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汉书》本传) 是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战国以来,各派知识人对于“天”大致仅作一般的肯定,而不作系统的解释。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 荀子则更为极端,认为“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篇》) 。虽然先秦各家对于“天”的理解颇有不同,但他们追求“道”都不直接诉诸“天”,而是从“心”下手。
……
我们可以说中国知识人特别注重精神修养,主要是为了保证“道”的庄严和纯一。内向超越的中国知识人,既没有教会可以依靠,也没有系统的“教条”(dogmas) 可资凭借。“正统”和“异端”在中国是缺乏客观标准的。朱熹和陆象山不是曾互斥对方为“异端”吗?王阳明和他的门人不是曾提倡过“三教合一”吗?所以“道”的唯一保证,便是每一个知识人的内心修养,虽然是真是伪还得要由每个人自己来断定。
但是中国知识人,特别是儒家,强调“道”,甚至提倡“道统”还有另一个重大的意义。他们是要以超世间的“道”和世间的“势”——主要是君主的政权——相抗衡。孟子最早已指出:
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尽心上》)
这样,“道”与“势”的紧张关系便由孟子拉开了历史的序幕。知识人必须以“道”自任和自重,不能为了求富贵之故,向王侯臣服,这是儒家的一贯立场。陈代劝孟子去谒见诸侯,多少可以施展一点自己的理想。“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孟子坚决地回答他:
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是不能让“道”受屈枉的。知识人最大的弱点是抵抗不住世间权势的诱惑。所以公孙丑问他,如果齐国给你老先生以卿相之位,使你可以“行道”,你动不动心呢?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公孙丑上》) 接着便是孟子讲他怎样“善养吾浩然之气”,然后才能达到“不动心”的境界。这一段话最能说明先秦知识人的“治气养心”是为了保证他们“心”中的“道”的坚贞。只有持此超世间的“道”,他们才能面对世间的“势”而不为所动。荀子也说:
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荀子·修身篇》)
这是荀子告诉我们,知识人为什么必须“修身”、必须“治气养心”。
以“道统”来驯伏“治统”,是后世儒家知识人所最为重视的一件大事。这是中国超世间的理想在世间求取实现的唯一途径。宋明理学的积极意义也在这里。吕坤说得最明白:
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呻吟语全集》卷一之四)
为了保持“理”的尊严,中国知识人是不能不讲心性修养的。否则“理”又何能不为“势”所夺?更何能使“理”常伸于天下万世?这是“内向超越”的知识人,在传统格局下的唯一出路。
论教育与反真女权
- 概述
- 目录
- 自撰序言
- 严正声明
- 第一章 两性智商均值差异与“变异性”的差异
- 第二章 基于考试成绩,经济社会环境,教育资源,时代背景等方面情况针对考试成绩性别差异的全方位解析
- 第三章 纠正概念错误,语言腐败,并示例如何打假
- 第四章 相关数据附录
- 结语
概述
书名:论教育与真女权——基于中外数据与科学事实的解析
作者:东风破云起苍黄(知乎网名)
周官学社出品
本书致敬先贤米塞斯、哈耶克、科尔奈否定计划经济的伟大贡献
第一版 完稿于耶元2023年
女权分子爱造谣“男女比例失衡”比如男比女多三千万来搞饥饿营销,实际上22岁左右的青年男女中女性稍微多一点。大陆官方没有找专家出来辟谣,说明这确实是个谣言,是个符合官方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谣言。毕竟按照政治学第一定律,只有官方否认的才可信(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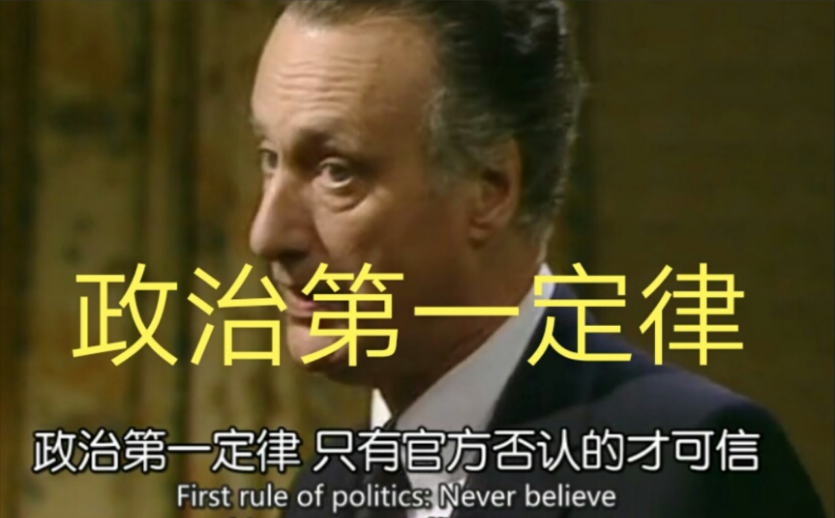
本书唯一的缺点就是尬吹太平天国邪教倡乱。洪秀全信的就是“爷火华”,不是昊天上帝。。。只不过洪秀全文化水平太低,只读过一本《劝世良言》小册子,胡言乱语之下还是只能直接偷偷摸摸地翻看《周礼》之类的书给自己的大脑“充电”,偶尔提及几句“皇天上帝”纯粹是胡思乱想搞缝合的结果。“一代领导核心”就是成功的洪秀全,洪秀全就是失败的“一代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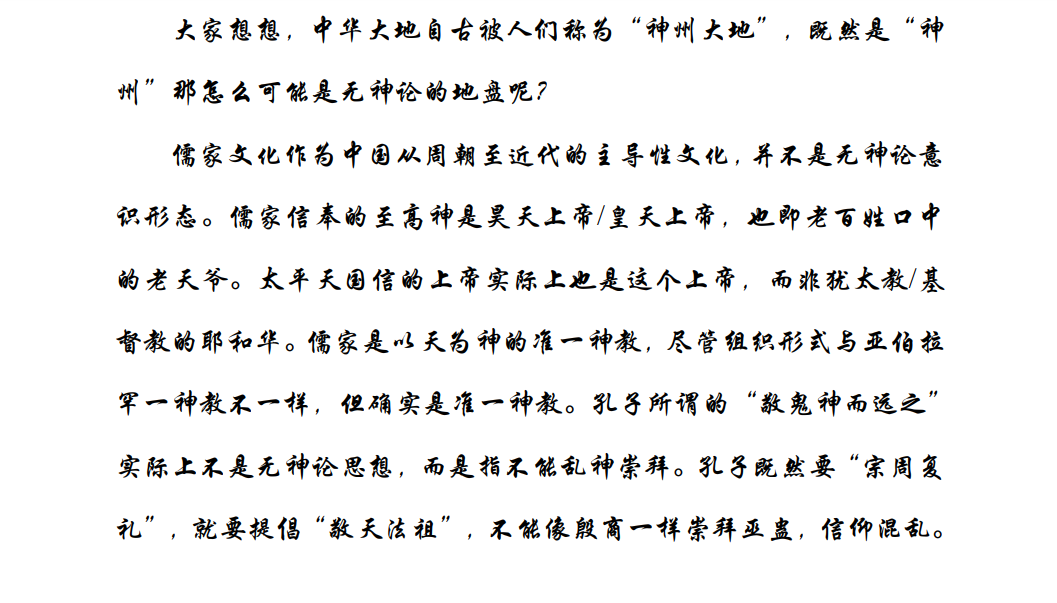
下面内容节选自《关于洪秀全“丁酉异梦”的互文性考辨》(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褚潇白2019-08-14 15:27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7期):
梁发在《劝世良言》开篇中说,神爷火华所创万物中有一自化为蛇魔的罪恶之神,引诱一妇人吞食知恶果,妇人又让其夫食之,故神爷火华发怒将二人逐出所居乐园。在乐园东边,神爷火华命令“基路伯”手握发火的剑警戒看护乐园,阻止那对夫妇重返乐土。这段故事出自《新旧约全书·创世记》,但关于伊甸园之蛇为蛇魔一说,乃是梁发自己的解释。在《劝世良言》第三篇中,可能是为了强调这个人类堕落故事的重要性,梁发又以不同的叙事方式把这个故事重复了一遍,其中与上帝作对的仍然是被称为恶魔的蛇。巧合的是,洪秀全那年生病时,神游四方,常在其室内走动跳跃,或如兵士战斗状,常大声疾呼:“斩妖,斩妖,斩呀!斩呀!这里有一只,那里有一只,没有一只可以挡我的宝剑一斫的。”这是洪仁玕日后讲给传教士韩山文的情节。在《太平天日》中,洪秀全叙述在异梦中与“天父上主皇上帝”相见后被指点凡间“妖魔迷害人情状”,并受命“战逐妖魔”,还被赐予了金玺。其中有不少战妖斩妖的情节,比如:
主(引者按:指洪秀全)与妖魔战时,天父上主皇上帝在其后,天兄基督亦在其后执金玺照妖。妖不能害主,且妖不敢见金玺,见金玺即走。其妖头甚作怪多变,有时打倒地,倏变为大蛇矣;又将大蛇打倒,倏又变为别样矣,能变得十七八变,虽狗虱之小亦能变焉。主战到愤怒时欲遽收他,天父上主皇上帝谕曰:“这妖是老蛇,能迷人食人灵魂,若即收他,许多被他食之灵魂无救矣,况污秽圣所,故暂容他命。”
此处出现之妖乃是“老蛇”,洪秀全已经将《劝世良言》中出现的蛇魔与他异梦中打斗的妖魔之间画上了等号。由于梁发在书中痛斥、攻击中国人之偶像崇拜和巫术风水等信仰风俗,并特别指出“蛇魔邪神以邪风迷蒙了灵心,不由正道之理、不安命守分,自为妄想”,所以,洪秀全在读了《劝世良言》后就开始铲除各种偶像:先除去了私塾里的孔子牌位,继而又开始讨伐佛、道及各种民间信仰庙宇(比如赐谷村“六窝庙”和象州“甘王庙”)内的塑像。在其后的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这种对于寺庙神像的攻击都是不遗余力的。不仅如此,由于梁发采用的《新旧约全书》译本将魔鬼撒旦翻译为“阎罗妖”或者“东海龙王”,所以太平天国也采用了“阎罗妖”的叫法,比如在1848年的《天兄圣旨》中,天兄基督晓谕天王时就说:“海龙就是妖魔头,凡间所说阎罗妖正是他,东海龙妖也是他,总是他变身,缠捉凡间人灵魂。”值得注意的是,龙也是皇帝的象征。1849年底或1850年初,洪秀全已将统治中国的满人及其官府爪牙定为应予消灭的妖魔。这个对于妖魔的身份确认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贯彻首尾。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也开始做梦,而且也梦到了蛇妖怪,由此与父亲的“丁酉异梦”相印证。洪天贵福预言1860年太平军第二次解南京之围,梦到两条蛇绕城,他用剑杀了蛇。洪秀全大喜,为庆祝梦的应验,特立节日以纪念。
注:上文修改了一个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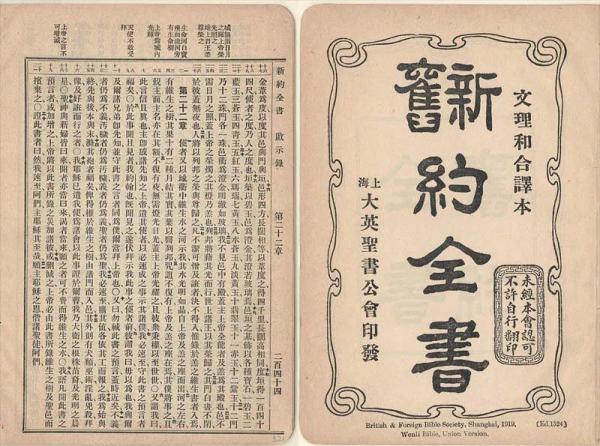
目录
自撰序言
开篇即点题:反女权的希望在于反真女权,反真女权的希望在于反对半边天主义,否定妇女解放,清算男女平等,为父权制正名。
针对半边天主义的否定,在体能的性别差异方面较为容易,而在文化教育/智能方面却显得十分困难,反女权人士在这方面的奔走呼号常常显得近乎愚蠢,甚至像是在给形形色色的女权主义者“ 递刀子”。在二战后,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诸如女性大学入学人数超过男性,公务员考试上岸人数女多男少,公检法被女性“ 占领” 之类的的现象,左派欢呼于女性似乎将要在后工业革命乃至信息化时代取得相对男性的社会竞争优势,从而一举推翻父权制,实现所谓的“ 全人类的解放” 。许多保守主义者对此感到极为恐慌,害怕左派,女权主义者以解放女性,解放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的旗号破坏人类文明的根基——父权制,彻底毁灭我们的祖先数千年来薪火相传,含辛茹苦建立起来的人类文明社会。
面对这一为许多人所恐慌的“难题” ,鄙人不才,决定挺身而出,冒天下之大不韪,承受左派和许多不明真相者的谩骂,以中外许许多多的数据与科学事实为基础,从被左派污染的媒体宣传和学界论文当中抽丝剥茧,还原真相,完全意义上的解构真女权,解构半边天,为一切有良知的保守主义者在光复之后重建能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民族/异性恋/农本位/市场经济/保守主义的文明社会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严正声明
第一章 两性智商均值差异与“变异性”的差异
1.1 智商均值差异
1.2 男女智力变异性存在差异
1.2.1智商离散度差异——男大女小
1.2.2 潜能发挥稳定性的性别差异
1.2.3 幼态与成年个体的两性变异性差异
1.2.4 男女智力差异的遗传学基础
第二章 基于考试成绩,经济社会环境,教育资源,时代背景等方面情况针对考试成绩性别差异的全方位解析
2.1 前提条件——已确定 21 世纪初中美两国基础教育资源女多男少
2.1.1 21 世纪初的中国已经出现基础教育资源女多男少的局面
2.1.2 21 世纪初的美国在大学录取时不惜以破坏人才选拔的公平性来优待女生和少数族裔
2.2 从中美高等院校入学考试对比分析看利女化的考试改革
2.2.1从美国 SAT/ACT考试看美国“ 高考”的利女化改革
2.2.2解析 1999 年扩招后高考利女腐化的原理与结果
2.2.3 从山东 3 + 3 高考结果的定量分析展望 3 + 1 + 2 与 3 + 3 时代高考与出生人口的关系
2.2.4 20世纪80 -- 90年代高考难度与长辈对那时候高考的回忆
2.3 谈经济驱动力的性别差异以及这种性别差异导致的男女入学率与智力分布曲线的偏离
2.4 公务员考试与考研/GRE考试当中的性别差异
2.4.1 公务员考试“女强男弱”的假象从何而来?
2.4.2 考研与GRE考试:扩招时代男生的考试能力更强但被录取人数更少
2.5细论扩招的危害/兼论米格道女本位周期律
2.5.1 扩招分流的那些差生如果参加入学考试会不会导致入学考试平均分女高男低?
2.5.2 与扩招相匹配的教材阉割导致“减负减负,越减越负”
2.5.3 扩招与劣化的教育改革相辅相成
2.5.4 扩招与“假就业”的自锁正反馈
2.5.5 美国大学扩招后的那些恶劣后果
2.5.6 谈米格道女本位周期律理论模型
2.6劣化生育的隐忧:人类遗传智商降低且女性可能降低更多
第三章 纠正概念错误,语言腐败,并示例如何打假
3.1对21世纪前三十年中国大陆真实总人口和性别比数据的讨论
3.2清理语言腐败,更正错误概念,恢复常识,澄清真相
3.3示例:对女权虚假学术和媒体宣传的打假
3.3.1 与考研逻辑不同,理科竞赛女生“ 录报比” 高于男生不能说明女生比男生更擅长理科
3.3.2 第一位程序员是女性说明男性计算机能力差于女性,抢夺了女性程序员的贡献吗?
3.3.3 记两则令人匪夷所思的女权主义理工科新闻报道
3.3.4对标中考的PISA数学成绩无性别差异?统计学把戏而已
3.3.5 如何看待数据帝发视频为张桂梅撑腰:「张桂梅帮助的不止女生」?(前后共三次拉锯反驳)
3.3.6 揭露女权主义对两性成绩差异的造假——以网易数读女权文章为例
第四章 相关数据附录
4.1各科目平均分性别差异与科目平均分的关系
4.1.1美国SAT考试(时间为1972——2014年)
4.1.2高考浙江卷除数学外的所有科目(时间为2006 -- 2014年)
4.1.3 浙江卷高考数学(2006——2014 年)+ 2016 六省全国卷高考理科数学 + 河南省S县05/06/09三年全国一卷数学
4.2高考状元男女比例与数量变迁
4.3 PRC 大规模城市化前对各地区定居人口儿童智商的测试数据
4.4山东省 3 + 3 高考全省前五十名男女比例
4.5 广东省更换全国卷前后极高分段男女比例变化的具体统计结果
结语
古人云:“晋之妇教,最为衰弊” 。晋武帝时期的司法也出现了给女性罪犯轻判的案例。西晋短暂的统一了中国约五十年时间,中国北方就沦陷于五胡十六国的胡尘里。
古希腊的斯巴达,以及西罗马帝国晚期也出现了生育率低,女权冲击司法之类的现象,最终古希腊,古罗马都亡于异族入侵。
亚里士多德曾经在《政治论》当中明确的指出,女权主义,以女制男是僭主政治,而非社会治理的康庄大道。
在这个 2023 年的进步主义衰世,各国的财政,人口,外贸等方方面面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三世纪到五世纪的东亚与西欧都是遍地腥膻,而现如今的所谓雅尔塔体系“ 后现代社会” 也出现了同样的日薄西山之兆,女权社会的秩序已经开始摇摇欲坠。
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在东亚巍然屹立了五千年。我们有责任擎起文明的火炬,保卫并延续祖先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文明。而想保卫我们汉族之中华的血脉与文明,我想,只有这一个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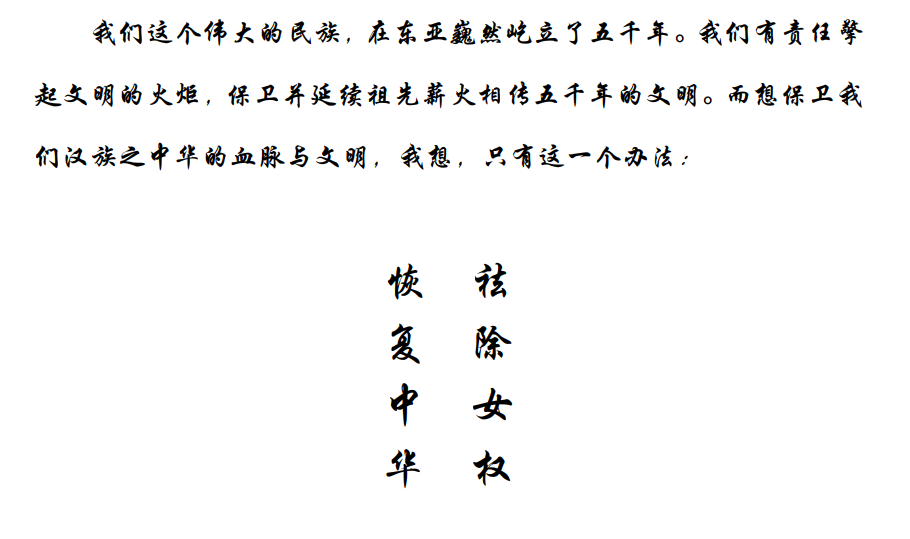
独裁者手册:为什么坏的行为几乎总是好的政治
- 简介
- 引 言 统治的规则
- 第一章 政治的法则 Chapter 1 - The Rules of Politics
- Three Political Dimensions
- Virtues of 3 - D Politics
- Change the Size of Dimensions and Change the World
- Rules Ruling Rulers
- Taxing
- Shuffling the Essential Deck
- Do the Rules Work in Democracies?
- 第二章 上台 Chapter 2 - Coming to Power
- Paths to Power with Few Essentials
- Speed Is Essential
- Pay to Play
- Mortality: The Best Opportunity for Power
- Inheritance and the Problem of Relatives
- Papal Bull - ying for Power
- Seizing Power from the Bankrupt
- Silence Is Golden
- Institutional Change
- Coming to Power in Democracy
- Democracy Is an Arms Race for Good Ideas
- Coalition Dynamics
- A Last Word on Coming to Power: The Ultimate Fate of Sergeant Doe
- 第三章 掌权 Chapter 3 - Staying in Power
- 第四章 窃贫济富 Chapter 4 - Steal from the Poor, Give to the Rich
- 第五章 获取与花费 Chapter 5 - Getting and Spending
- 第六章 腐败使人有权 绝对的腐败绝对使人有权 Chapter 6 - If Corruption Empowers, Then Absolute Corruption Empowers Absolutely
- 第七章 对外援助 Chapter 7 - Foreign Aid
- 第八章 反叛中的人民Chapter 8 - The People in Revolt
- 第九章 战争,和平与世界秩序 Chapter 9 - War, Peace, and World Order
- 第十章 怎么办?Chapter 10 - What Is To Be Done?
- 大陆版被删减内容
简介
英文名: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
作者: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lastair Smith
从管理一家公司、领导一个社会组织,到操纵一台政治机器,获得并保持权力的三个纬度、五个法则。
三个维度:
the nominal selectorate, the real selectorate, and the winning coalition
interchangeable, influential, and essential groups
五个法则:
Rule 1: Keep your winning coalition as small as possible. A small coalition allows a leader to rely on very few people to stay in power. Fewer essentials equals more control and contributes to more discretion over expenditures. Bravo for Kim Jong Il of North Korea. He is a contemporary master at ensuring dependence on a small coalition.
Rule 2: Keep your nominal selectorate as large as possible. Maintain a large selectorate of interchangeables and you can easily replace any troublemakers in your coalition, influentials and essentials alike. After all, a large selectorate permits a big supply of substitute supporters to put theessentials on notice that they should be loyal and well behaved or else face being replaced. Bravo to Vladimir Ilyich Lenin for introducing universal adult suffrage in Russia’s old rigged election system. Lenin mastered the art of creating a vast supply of interchangeables.
Rule 3: Control the flow of revenue. It’s always better for a ruler to determine who eats than it is to have a larger pie from which the people can feed themselves. The most effective cash flow for leaders is one that makes lots of people poor and redistributes money to keep select people—their supporters—wealthy. Bravo to Pakistan’s president Asif Ali Zardari, estimated to be worth up to $4 billion even as he governs a country near the world’s bottom in per capita income.
Rule 4: Pay your key supporters just enough to keep them loyal. Remember, your backers would rather be you than be dependent on you. Your big advantage over them is that you know where the money is and they don’t. Give your coalition just enough so that they don’t shop around for someone to replace you and not a penny more. Bravo to Zimbabwe’s Robert Mugabe who, whenever facing a threat of a military coup, manages finally to pay his army, keeping their loyalty against all odds.
Rule 5: Don’t take money out of your supporter’s pockets to make the people’s lives better. The flip side of rule 4 is not to be too cheap toward your coalition of supporters. If you’re good to the people at the expense of your coalition, it won’t be long until your “friends” will be gunning for you. Effective policy for the masses doesn’t necessarily produce loyalty among essentials, and it’s darn expensive to boot. Hungry people are not likely to have the energy to overthrow you, so don’t worry about them. Disappointed coalition members, in contrast, can defect, leaving you in deep trouble. Bravo to Senior General Than Shwe of Myanmar, who made sure following the 2008 Nargis cyclone that food relief was controlled and sold on the black market by his military supporters rather than letting aid go to the people—at least 138,000 and maybe as many as 500,000 of whom died in the disaster.
引 言 统治的规则
政治核心:获得并保持权力
确保政治生存的最好方式是只依靠少数人来上位和在位。
最高统治阶层可以拥有如何花钱和如何征税的自由裁量权
第一章 政治的法则 Chapter 1 - The Rules of Politics
Three Political Dimensions
the nominal selectorate, the real selectorate, and the winning coalition
interchangeable, influential, and essential groups
Virtues of 3 - D Politics
Governments do not differ in kind. They differ along the dimensions of their selectorates and winning coalitions.
Change the Size of Dimensions and Change the World
Any leader worth her salt wants as much power as she can get, and to keep it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Managing the interchangeables, influentials, and essentials to that end is the act, art, and science of governing.
Rules Ruling Rulers
The answer, for any savvy politician, depends on how many people the leader needs to keep loyal—that is, the number of essentials in the coalition.
Taxing
As a result, heads of governments reliant on a large coalition tend not to be among the world’s best paid executives.
This means that the next step in explaining the calculus of politics is to figure out how much a leader can keep and how much must be spent on the coalition and on the public if the incumbent is to stay in power.
Shuffling the Essential Deck
Rule 1: Keep your winning coalition as small as possible. A small coalition allows a leader to rely on very few people to stay in power. Fewer essentials equals more control and contributes to more discretion over expenditures. Bravo for Kim Jong Il of North Korea. He is a contemporary master at ensuring dependence on a small coalition.
Rule 2: Keep your nominal selectorate as large as possible. Maintain a large selectorate of interchangeables and you can easily replace any troublemakers in your coalition, influentials and essentials alike. After all, a large selectorate permits a big supply of substitute supporters to put theessentials on notice that they should be loyal and well behaved or else face being replaced. Bravo to Vladimir Ilyich Lenin for introducing universal adult suffrage in Russia’s old rigged election system. Lenin mastered the art of creating a vast supply of interchangeables.
Rule 3: Control the flow of revenue. It’s always better for a ruler to determine who eats than it is to have a larger pie from which the people can feed themselves. The most effective cash flow for leaders is one that makes lots of people poor and redistributes money to keep select people—their supporters—wealthy. Bravo to Pakistan’s president Asif Ali Zardari, estimated to be worth up to $4 billion even as he governs a country near the world’s bottom in per capita income.
Rule 4: Pay your key supporters just enough to keep them loyal. Remember, your backers would rather be you than be dependent on you. Your big advantage over them is that you know where the money is and they don’t. Give your coalition just enough so that they don’t shop around for someone to replace you and not a penny more. Bravo to Zimbabwe’s Robert Mugabe who, whenever facing a threat of a military coup, manages finally to pay his army, keeping their loyalty against all odds.
Rule 5: Don’t take money out of your supporter’s pockets to make the people’s lives better. The flip side of rule 4 is not to be too cheap toward your coalition of supporters. If you’re good to the people at the expense of your coalition, it won’t be long until your “friends” will be gunning for you. Effective policy for the masses doesn’t necessarily produce loyalty among essentials, and it’s darn expensive to boot. Hungry people are not likely to have the energy to overthrow you, so don’t worry about them. Disappointed coalition members, in contrast, can defect, leaving you in deep trouble. Bravo to Senior General Than Shwe of Myanmar, who made sure following the 2008 Nargis cyclone that food relief was controlled and sold on the black market by his military supporters rather than letting aid go to the people—at least 138,000 and maybe as many as 500,000 of whom died in the disaster.
Do the Rules Work in Democracies?
Why, for example, does Congress gerrymander districts? Precisely because of Rule 1: Keep the coalition as small as possible.
Why do some political parties favor immigration? Rule 2: Expand the set of interchangeables.
Why are there so many battles over the tax code? Rule 3: Take control of the sources of revenue.
Why do Democrats spend so much of that tax money on welfare and social programs? Or why on earth do we have earmarks? Rule 4: Reward your essentials at all costs.
Why do Republicans wish the top tax rate were lower, and have so many problems with the idea of national health care? Rule 5: Don’t rob your supporters to give to your opposition.
路易十四财政破产:无法用必要的资源继续收买核心支持者,不在于必须削减公共开支。只要支持他更加有利可图,那就会继续获得必要的忠诚!
The lessons from both extremes apply—whether you’re talking about Saddam Hussein or George Washington. After all, the old saw still holds true—politicians are all the same.
第二章 上台 Chapter 2 - Coming to Power
Damn the idea of good governance and don’t elevate the concerns of the people over your own and those of your supporters: That’s a good mantra for would-be dictators. In such a way any John Doe—even a Samuel Doe—can seize power, and even keep it.
Paths to Power with Few Essentials
To come to power a challenger need only do three things. First, he must remove the incumbent. Second, he needs to seize the apparatus of government. Third, he needs to form a coalition of supporters sufficient to sustain him as the new incumbent. Each of these actions involves its own unique challenges. The relative ease with which they can be accomplished differs between democracies and autocracies.
That is, the general rule of thumb for rebellion is that revolutions occur when those who preserve the current system are sufficiently dissatisfied with their rewards that they are willing to look for someone new to take care of them. On the other hand, revolts are defeated through suppression of the people—always an unpleasant task—so coalition members need to receive enough benefits from their leader that they are willing to do horribly distasteful things to ensure that the existing system is maintained. If they do not get enough goodies under the current system, then they will not stop the people from rising up against the regime.
Speed Is Essential
Once the old leader is gone, it is essential to seize the instruments of power, such as the treasury,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hi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small coalition systems. Anyone who waits will be a loser in the competition for power.
This is why it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to seize the reins of power quickly to make sure that your group gets to control the instruments of the state, and not someone else’s.
Pay to Play
Paying supporters, not good governance or representing the general will, is the essence of ruling. Buying loyalty is particularly difficult when a leader first comes to power. When deciding whether to support a new leader, prudent backers must not only think about how much their leader gives them today. They must also ponder what they can expect to receive in the future.
Allaying supporters’ fears of being abandoned is a key element of coming to power. Of course, supporters are not so naïve that they will be convinced by political promises that their position in the coalition is secure. But such political promises are much better than tipping your hand as to your true plans. Once word gets out that supporters are going to be replaced, they will turn on their patron.
Leaders understand the conditions that can cost them their heads. That is why they do their level best to pay essential cronies enough that these partners really want to stay loyal. This makes it tough for someone new to come to power.
Mortality: The Best Opportunity for Power
Impending death often induces political death. The sad truth is that if you want to come to power in an autocracy you are better off stealing medicalrecords than you are devising fixes for your nation’s ills.
Inheritance and the Problem of Relatives
Once an incumbent is dead, there is still the issue of fending off competitors for the dead leader’s job. Ambitious challengers still need to grab control of the state apparatus, reward supporters, and eliminate rivals.
In practice this meant grabbing the treasury and paying off the army.
Would-be autocrats must be prepared to kill all comers—even members of the immediate family.
If you are a prince and you want to be king, then you should do nothing to dissuade your father’s supporters of their chances of being important to you too. They will curry favor with you. You should let them. You will need them to secure a smooth transition. If you want them gone (and you may not), then banish them from court later. But the first time they need to know your true feelings for them is when you banish them from court, well after your investiture and not a minute before.
Papal Bull - ying for Power
But remember, what constitutes doing the right thing must be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potential supporter; it ma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what is best for a community or nation. Anyone who thinks leaders do what they ought to do—that is, do what is best for their nation of subjects—ought to become an academic rather than enter political life. In politics, coming to power is never about doing the right thing. It is always about doing what is expedient.
Seizing Power from the Bankrupt
As it turns out, one thing that is always expedient is remaining solvent. If a ruler has run out of money with which to pay his supporters, it becomes far easier for someone else to make coalition members an attractive offer. Financial crises are an opportune time to strike.
His mistake was operating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which necessitated a large coalition, and implementing an unpopular policy—continuing the czar’s war—thereby alienating his coalition right from the start. Lenin and the Bolsheviks made no such mistakes.
Successful leaders must learn the lesson of these examples and put raising revenue and paying supporters above all else.
Silence Is Golden
We all grew up hearing the lesson that silence is golden. As it turns out, violating that basic principle is yet another path by which incumbents can succumb to their political rivals.
The incumbent’s advantage in offering rewards disappears as soon as coalition members come to suspect their long run access to personal benefits will end. An incumbent’s failure to reassure his coalition that he will continue to take care of them provides competitors with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seize power.
Silence, as Ben Bella learned far too late, truly is golden. There is never a point in showing your hand before you have to; that is just a way to ensure giving the game away.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re is a common adage that politicians don’t change the rules that brought them to power. This is false. They are ever ready and eager to reduce coalition size. What politicians seek to avoid are any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at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eople to whom they are beholden. Yet much as they try to avoid them, circumstances do arise when institutions must become more inclusive. This can make autocrats vulnerable because the coalition they have established and the rewards they provide are then no longer sufficient to maintain power.
叶利钦要削减官僚特权,官僚担心丧失特权会反对改革。改革要确保政权稳固,不可贪功冒进。
Yeltsin was, as it turned out, much better at working out how to come to power than he was at governing well, but that is a tale for another time.
Coming to Power in Democracy
Challengers succeed when they offer better rewards than the government. Given that there are so many who need rewarding, this means coming up with better or at least more popular public policies. Unfortunately, because it is easy to erode the support of the incumbent’s coalition, it remains difficult for the challenger to pay off her own supporters.
Democratic Inheritance
Of course, dynastic rule is more common outside of democracy. Even if you don’t have the good fortune to be born into a political dynasty, you can come to power in a democracy if you have good, or at least popular, ideas. Good ideas that help the people are rarely the path to power in a dictatorship.
Democracy Is an Arms Race for Good Ideas
But past deeds don’t buy loyalty. When a rival appears with a cheaper way to fix the environment, or the rival finds policy fixes for other problems that people care about more, then the rival can seize power through the ballot box. Autocratic politics is a battle for private rewards. Democratic politics is a battle for good policy ideas. If you reward your cronies at the expense of the broader public, as you would in a dictatorship, then you will be out on your ear so long as you rely on a massive coalition of essential backers.
Coalition Dynamics
Divide and conquer is a terrific principle for coming to power in a democracy—and one of the greatest practitioners of this strategy was Abraham Lincoln, who propelled himself to the US presidency by splitting the support for the Democratic Party in 1860.
In democracies, politics is an arms race of ideas. Just as the democrat has to be responsive to the people when governing, when seeking office it helps to propose policies that the voters like and it pays to want to do more (as opposed to less)—even if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are damaging down the road (when you’re no longer in office). Satisfy the coalition in the short run. When democratic politicians lament “mortgaging our children’s future,” they’re really regretting that it was not them who came up with the popular policy that voters actually want.
A Last Word on Coming to Power: The Ultimate Fate of Sergeant Doe
Although dressed up in many forms, successful challengers follow basic principles. They offer greater expected rewards to the essential supporters of the current leader than those essentials currently receive. Unfortunately for the challenger, the incumbent has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because the members of the established winning coalition can be confident that their leader will keep on lining their pockets or providing the public policies they want. But if the incumbent is known to be dying, takes too much for himself, chooses the wrong policies, or is seen to have only weak loyalty from his critical backers, then the door swings wide open for a challenger to step in and depose the incumbent.
To achieve power means recognizing the moment of opportunity, moving fast, and moving decisively to seize the day. And, for good measure, coming to power also means seizing any opponents, figuratively in democracies, and physically in dictatorships. Coming to power is not for the faint of heart.
Politics, however, does not end with becoming a leader. Even as you take up the reins of power and enjoy its rewards, others are gunning for you. They want the same job that you so desperately sought! Politics is a risky business. As we will see, successful leaders manage these risks by locking in a loyal coalition. Those who fail at this first task open the door for someone else to overthrow them.
第三章 掌权 Chapter 3 - Staying in Power
What, then, must a newly minted leader do to keep his (or her) head? A good starting place is to shore up the coalition of supporters.
A prudent new incumbent will act swiftly to get some of them out of the way and bring in others whose interests more strongly assure their future loyalty. Only after sacking, shuffling, and shrinking their particular set of essentials can a leader’s future tenure be assured.
Governance in Pursuit of Heads
This is the essential lesson of politics: in the end ruling is the objective, not ruling well.
The Perils of Meritocracy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a coalition are: (1) Loyalty; (2) Loyalty; (3) Loyalty. Successful leaders surround themselves with trusted friends and family, and rid themselves of any ambitious supporters.
Keep Essentials Off-Balance
The essence of keeping coalition members off-balance is to make sure that their loyalty is paid for and that they know they will be ousted if their reliability is in doubt.
Democrats Aren’t Angels
Leaders never hesitate to miscount or destroy ballots. Coming to office and staying in offic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n politics. And candidates who aren’t willing to cheat are typically beaten by those who are.Since democracies typically work out myriad ways to make cheating difficult, politicians in power in democracies have innovated any number of perfectly legal means to ensure their electoral victories and their continued rule.
One counterintuitive strategy is for leaders to encourage additional competitors.
Bloc Voting集团投票
The raja understood that he could manipulate his bloc of backers to make and break governments and, in doing so, he could enrich himself a lot and help his followers a little bit in turn.
By rewarding supportive groups over others, individual voters are motivated to follow the choice of their group leader,
Of course, leaders can use sticks as well as carrots.Lee Kuan Yew ruled Singapore from 1959 until 1990, making him, we believe, the longest serving prime minister anywhere. His party,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dominated elections and that dominance was reinforced by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housing, upon which most people in Singapore rely. Neighborhoods that fail to deliver PAP votes come election time found the provision and maintenance of housing cut off.
Leader Survival
Building a small coalition is key to survival. The smaller the number of people to whom a leader is beholden the easier it is for her to persist in office. Autocrats and democrats alike try to cull supporters. It remains very difficult to measure the size of coalitions precisely.
Staying in power right after having come to power is tough, but a successful leader will seize power, then reshuffle the coalition that brought him there to redouble his strength. A smart leader sacks some early backers, replacing them with more reliable and cheaper supporters. But no matter how much he packs the coalition with his friends and supporters, they will not remain loyal unless he rewards them.
第四章 窃贫济富 Chapter 4 - Steal from the Poor, Give to the Rich
贫富交换,换得支持,轻赏重罚,参考商鞅韩非
“Knowing where the money i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autocracies—and particularly difficult. Such systems are shrouded in secrecy. Supporters must be paid but there are no accurate accounts detailing stocks and flows of wealth. Of course, this lack of transparency is by design. 1 Thus does chaotic bookkeeping become a kind of insurance policy: it becomes vastly more difficult for a rival to promise to pay supporters if he cannot match existing bribes, or, for that matter, put his hands on the money. Indeed, secrecy not only provides insurance against rivals, it also keeps supporters in the dark about what other supporters are getting.
Secrecy ensures that everyone gets the deal they can negotiate, not knowing how much it might cost to replace them. Thus every supporter’s price is kept as low as possible, and woe to any supporter who is discovered trying to coordinate with his fellow coalition members to raise their price.
Little surprise, then, that we so often see looting, confiscations, extraction, and fire sales during political transitions, or conversely, and perhaps ironically, temporary liberal reforms by would-be dictators who are mindful that it is easier for a public goods–producing democrat than an autocrat to survive the first months in office.
Because democracies have well-organized and relatively transparent treasuries, their flow of funds is left undisturbed by leader turnover.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this transparency. First, as we are about to explore, democratic leaders best promote their survival through policies of open government. Second, a larger proportion of revenue in democracies than in autocracies tends to be from the taxation of people at work. Such taxes need to be levied in a clear and transparent way, because just as surely as leaders need money, their constituents want to avoid taxes.
Taxation
Somewhere between these extremes there is an ideal tax rate that produces the most revenue the state can get from taxation. What that ideal rate is depends on the precise size of the winning coalition.
However, crucially, in democracies it is the coalition’s willingness to bear taxes that is the true constraint on the tax level.
Democrats tax heavily too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as autocrats: they provide subsidies to groups that favor them at the polls at the expense of those who oppose them.
While all leaders want to generate revenue with which to reward supporters, democratic incumbents are constrained to keep taxes relatively low. A democrat taxes above the good governance minimum, but he does not raise taxes to the autocrat’s revenue maximization point.
In autocracies, it is unwise to be rich unless it is the government that made you rich. And if this is the case, it is important to be loyal beyond all else.
Tax Collectors
As for all the rules and exceptions that make the US tax code so complicated, these inevitably result from politicians doing what politicians inevitably do: rewarding their supporters at the expense of everybody else.
The first rule of office holding is to minimize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se support you need. To avoid becoming a slave of their own tax collectors, autocrats often use indirect taxation instead. With indirect taxes, the cost of the tax is passed on to someone other than the person actually paying it.
Privatized Tax Collection
Autocrats can avoid th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of gathering and redistributing wealth by authorizing their supporters to reward themselves directly. For many leaders, corruption is not something bad that needs to be eliminated. Rather it is an essential political tool. Leaders implicitly or sometimes even explicitly condone corruption. Effectively they license the right to extract bribes from the citizens.
Extraction
The resource curse enables autocrats to massively reward their supporters and accumulate enormous wealth.
This effect is much less pernicious in democracies. The trouble is that once a state profits from mineral wealth, it is unlikely to democratize. The easiest way to incentivize the leader to liberalize policy is to force him to rely on tax revenue to generate funds. Once this happens, the incumbent can no longer suppress the population because the people won’t work if he does.
Effective taxation requires that the people are motivated to work, but people cannot produce as effectively if they are forbidden such freedoms as freedom to assemble with their fellow workers and free speech—with which to think about, among other things, how to make the workplace perform more effectively, and how to make government regulations less of a burden on the workers.
Borrowing
分摊成本,转移压力
A leader should borrow as much as the coalition will endorse and markets will provide. There is surely a challenger out there who will borrow this much and, in doing so, use the money to grab power away from the incumbent. So not borrowing jeopardizes a leader’s hold on power. Heavy borrowing is a feature of small coalition settings.
In an autocracy, the small size of the coalition means that leaders are virtually always willing to take on more debt. The only effective limit on how much autocrats borrow is how much people are willing to lend them.
Markets limit how much a nation can borrow. If individuals borrow too much and either cannot or will not repay it, then banks and other creditors can seize assets to recover the debt.
Nevertheless, this has a profound effect, as the ability to engage in borrowing in financial markets is valuable. For this reason nations generally pay their debt.
As in the Nigerian case, the discovery of exploitable natural resources provides one means to increase debt service and hence more borrowing. However, without such discoveries, the only way to increase borrowing is to increase tax revenue. For autocratic leaders this means liberalizing their policies to encourage people to work harder because they already tax at a high (implicit) rate. Only when facing financial problems are leaders willing to even consider undertaking such politically risky liberalization. They don’t do it frequently or happily. They liberalize, opening the door to a more democratic, representative and accountable government only when they have no other path to save themselves from being deposed today.
Debt Forgiveness
债务减免无效甚至有害
Even though debt-reduction programs vet candidates, these examples suggest that in many cases for-giveness without institutional reform simply allows leaders to start borrowing again.
That is, we turn for the moment to thinking about how we can use the logic of dictatorial rule to give autocrats the right incentives to change their government for the better. We wonder, can we create a desire by at least some autocrats to govern for the people as the best way to ensure their own political survival?
We know that debt relief allows autocrats to entrench themselves in office. Debt forgiveness with the promise of subsequent democratization never works. An autocrat might be sincere in his willingness to have meaningful elections in return for funds. Yet o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is over and the leader can borrow to pay off the coalition, any promised election will be a sham. For democrats, debt relief, while helpful, is unnecessary. By eliminating debt relief for autocrats we can help precipitate the sorts of rebellions seen in the Middle East in 2011, rebellions that, as discussed later, may very well open the door to better governments in the future.
Taxation, resource extraction, and borrowing are the foremost ways of acquiring funds for enriching a coalition.
Leaders tax because they need to spend on their coalition. Successful leaders raise as much revenue as they can.
Having filled government coffers, leaders spend resources in three ways. First they provide public goods. That is, policies that benefit all. Second, they deliver private rewards to their coalition members.
第五章 获取与花费 Chapter 5 - Getting and Spending
Any new incumbent who wants to be around for a long time needs to fine-tune the art of spending money. Of course, he can err on the side of generosity to the coalition or to the people—but only with any money that is left for his own discretionary use after taking care of the coalition’s needs. He had better not err on the side of shortchanging anyone who could mount a coup or a revolution.
Effective Policy Need Not Be Civic Minded
It is true, as Hobbes’s believed, that happy, well-cared-for people are unlikely to revolt. China’s prolonged economic growth seems to have verified that belief (at least for now). Keep them fat and happy and the masses are unlikely to rise up against you. It seems equally true, however, that sick, starving, ignorant people are also unlikely to revolt.
It is the great in-between; those who are neither immiserated nor coddled. The former are too weak and cowered to revolt. The latter are content and have no reason to revolt. Truly it is the great in- between who are a threat to the stability of a regime and its leaders. Therefore, a prudent leader balances resources between keeping the coalition content and the people just fit enough to produce the wealth needed to enrich the essentials and the incumbent.
Leaders who depend on a large coalition have to work hard to make sure that their citizens’ lives are not solitary, nasty, poor, brutish, and short. That doesn’t mean democratic rulers have to be civic minded, nor would they need to harbor warm and cuddly feelings for their citizens. All they need is to ensure that there are ample public benefits to provide a high quality of life. They just need to follow the rules by which successful leaders rule, adapting them to the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that any democrat faces: being stuck with dependence on an unruly crowd of essentials to keep them in power.
The most reliable means to a good life for ordinary people remains the presence of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in the form of dependence on a big coalition that compels power-seeking politicians to govern for the people. Democracy, especially with little or no organized bloc voting, aligns incentives such that politicians can best serve their own self-interest, especially their interest in staying in office, by promoting the welfare of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people. That, we believe, is why most democracies are prosperous, stable, and secure places to live.
They resist the cry of people like us who demand improved governance before any bailout money is offered up to rescue a troubled autocratic economy.
Bailouts and Coalition Size
Therefore, financial crises and the need for a bailout are just about always bad news for democrats.
Is Democracy a Luxury?
Yes, the world has produced wise, well-intentioned leaders even among those who depend on few essentials, but it neither produces a lot of them nor does it ensure that they have good ideas about how to make life better for others. Indeed, a common refrain among small-coalition rulers is that the very freedoms, like free speech, free press, and especially freedom of assembly, that promote welfare-improving government policies are luxuries to be doled out only after prosperity is achieved and not before. This seems to be the self-serving claim of leaders who keep their people poor and oppressed.
No doubt it is good to be rich, and many of the world’s rich countries are democratic. But dependence on a large coalition of essentials is a powerful explanation of quality of life even when wealth is absent, just as it seems to be a harbinger of future wealth.
Public Goods Not for the Public’s Good
初级教育确保劳动力素质不至于太低
Highly educated people are a potential threat to autocrats, and so autocrats make sure to limit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Math and science are great subjects for study in China;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re the subjects of democracies.
Who Doesn’t Love a Cute Baby?
婴儿死亡率
Clean Drinking Water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As we’ve demonstrated, even a nasty dictator provides the people with basic education and essential health care so that they can work at making the autocrat rich.
Shoddy infrastructure is often an intentionally designed feature of many countries, not a misfortune suffered unwillingly.
Public Goods for the Public Good
It is surely no coincidence that all but one (Singapore) of the twenty-five countrie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ith the highest per capita incomes are liberal democracies; that is, societies that enjoy rule of law, with transparent and accountable government, a free press, and freedom of assembly. These are places that foster rather than suppress or obstruct political competition. They foster such competition not out of civicmindedness but rather out of the necessity of assembling a large coalition of supporters.
And being dependent on many essentials, all of these regimes share in common the provision of the cheap and yet hugely valuable public good called freedom.
Earthquakes and Governance
When there are lots of essential supporters, rescue is swift and repair is quick and effective. If it isn’t as swift and effective as people expect—and in large-coalition systems they expect it to be remarkably swift and effective— then political heads role.
第六章 腐败使人有权 绝对的腐败绝对使人有权 Chapter 6 - If Corruption Empowers, Then Absolute Corruption Empowers Absolutely
用贪官反贪官
Power and Corruption
Private Goods in Democracies
Private Goods in Small Coalition Settings
Wall Street: Small Coalitions at Work
Dealing with Good Deed Doers
Cautionary Tales: Never Take the Coalition for Granted
Whistle-blowing is not the only way to get in trouble. Leaders can put themselves at dire risk if they take their coalition’s loyalty for granted. The rules governing rulers teach us that leaders should never underpay their coalition whether they do so to reward themselves or the common people. Those who want to enrich themselves must do so out of discretionary funds, not coalition money. Those who want to make the people’s lives better likewise should only do so with money out of their own pockets and not at the expense of the coalition. Leaders sometimes miscalculate what is needed to keep the coalition happy. When they make this mistake it costs them their leadership role and, very often, their life.
Caesar made the mistake of trying to help the people by using a portion of the coalition’s share of rewards. It is fine for leaders to enrich the people’s lives, but it has to come out of the leader’s pocket, not the coalition’s. The stories of Caesar and Castellano remind us that too many good deeds or too much greed are equally punished if the coalition loses out as a result.
Discretionary Money
Discretion means leaders have choices. So far we have looked at leaders who use their discretion to enrich themselves but we do not mean to suggestthat people in power must be greedy louts like Marcos, Mobutu, Suharto, and Bashir.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for autocrats to be civic-minded, well-intentioned people, eager to do what’s best for the people they govern. The trouble with reliance on such well-intentioned people is that they are unconstrained by the accountability of a large coalition. It is hard for a leader to know what the people really want unless they have been chosen through the ballot box, and allow a free media and freely assembled groups to articulate their wishes. Without the accountability of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a free press, free speech, and freedom of assembly, even well-intentioned small-coalition rulers can only do whatever they and their coalition advisers think is best.
Most people think that reducing corruption is a desirable goal. One common approach is to pass additional legislation and increase sentences for corruption. Unfortunately such approaches are counterproductive. When a system is structured around corruption, everyone who matters, leaders and backers alike, are tarred by that corruption. They would not be where they were if they had not had their hand in the till at some point. Increasing sentences simply provides leaders with an additional tool with which to enforce discipline. It is all too common for reformers and whistle-blowers to be prosecuted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Legal approaches to eliminating corruption won’t ever work, and can often make the situation worse.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corruption is to change the underlying incentives. As coalition size increases, corruption becomes a thing of the past.
But make political leaders accountable to more people and politics becomes a competition for good ideas, not bribes and corruption.
第七章 对外援助 Chapter 7 - Foreign Aid
The Political Logic of Aid
Yet the people in recipient nations often develop a hatred for the donor. And recipient governments (and donors too) often have different views about what the money should be for. As we will see, democrats are constrained by their big coalition to do the right thing at home. However, these very domestic constraints can lead them to exploit the peoples of other nations almost without mercy.
The fact is, aid does a little bit of good in the world and vastly more harm.
The Impact of Aid
Example after example highlight the simple fact that aid is given in exchange for policy concessions far more readily and in far larger quantities than to reduce poverty and suffering.
An Assessment of Foreign Aid
What aid does well is help dictators cling to power and withhold freedom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have proven that they can effectively deliver basic health care and primary education.
Aid Shakedowns
Fixing Aid Policy
That’s probably true, but knowing how to fix local problems and having the will or interest to do so is quite another matter. This policy of giving money to recipients in anticipation of their fixing problems should stop. Instea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escrow money, paying it out only when objectives are achieved.
Nation Building
Dictators are cheap to buy. They deliver policies that democratic leaders and their constituents want, and being beholden to relatively few essential backers, autocrats can be bought cheaply. They can be induced to trade policies the democrat wants for money the autocrat needs. Buying democrats is much more expensive. Almost every US president has argued that he wants to foster democracy in the world. However, the same US presidents have had no problem undermining democratic, or democratizing, regimes when the people of those nations elect leaders to implement policies US voters don’t like.
In case after case, the story is the same. Democrats prefer compliant foreign regimes to democratic ones. Democratic interventionists, while proclaiming to be using military force to pursue democratization, have a profound tendency to reduce the degree of democracy in their targets, while increasing policy compliance by easily purchased autocrats.
Aid is a tool for buying influence and policy. Unless we the people really value development and are willing to make meaningful sacrifices towards those ends then aid will continue to fail in its stated goals. Democrats are not thuggish brutes. They just want to keep their jobs, and to do so they need to deliver the policies their people want. Despite the idealistic expressions of some, all too many of us prefer cheap oil to real change in West Africa or the Middle East. So we really should not complain too much when our leaders try to deliver what we want. That, after all, is what democracy is about.
第八章 反叛中的人民Chapter 8 - The People in Revolt
A SUCCESSFUL LEADER ALWAYS PUTS THE WANTS OF his essential supporters before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Without the support of his coalition a leader is nothing and is quickly swept away by a rival. But keeping the coalition content comes at a price when the leader’s control depends only on a few.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coalition’s members get paid at the cost of the rest of society.
To Protest or Not To Protest
If rule is really harsh, people are effectively deterred from rising up.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is the answer to when regimes choose the road to democracy rather than to sustained autocracy.
Nipping Mass Movements in the Bud
There are two diametrically opposed ways in which a leader can respond to the threat of a revolution. He can increase democracy, making the people so much better off that they no longer want to revolt. He can also increase dictatorship, making the people even more miserable than they were before while also depriving them of a credible chance of success in rising up against their government.
New leaders typically reshuffle their coalition, so key backers of the regime were uncertain whether they would be retained by the successor. Lacking assurance that they would continue to be rewarded they stood aside and allowed the people to rebel.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may seem spontaneous but we really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y arise when enough citizens believe they have a realistic chance of success. That is why successful autocrats make rebellion truly unattractive. They step in quickly to punish harshly those who first take to the streets.
A prudent dictator nips rebellion in the bud. That is why we have reiterated the claim that only people willing to engage in really nasty behavior should contemplate becoming dictators. The softhearted will find themselves ousted in the blink of an eye.
Protest in Democracy and Autocracy
In democracy, protest is about alerting leaders to the fact that the people are unhappy, and that, if changes in policy are not made, they’ll throw the rascals out. Yet in autocracy, protest has a deeper purpose: to bring down the very i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and change the way the people are governed.
Shocks Raise Revolts
Dead people cannot protest.
Are Disasters Always Disasters for Government Survival?
We believe this is the case because democratic leaders are supposed to deliver effective public policies, and those effective policies include ensuring good building codes are enforced and excellent rescue and recovery is implemented following a natural disaster. The death of many in such a disaster is a signal to everyone else that the leadership has not done an adequate job of protecting the people and so out go the leaders.
Responding to Revolution or Its Threat
Power to the People
The expansion of freedoms is a sure sign of impending democratization. Economic necessity is one factor that produces such a concession. Another is coming to power already on the back of a large coalition.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encourages entrepreneurial zeal, but it also protects the civil liberties of the people.
So the first policy recommendation for outside observers when a dictator faces national bankruptcy, and the protests likely to follow in its train is this: don’t save the dictator; don’t forgive indebtedness unless the dictator first actually puts his hold on power at real risk by permitting freedom of assembly, a free press, freedom to create opposition parties, and free, competitive elections in which the incumbent’s party is given no advantages in campaign funds, rallies, or anything else. Only after such freedoms and real political competition are in place might any debt forgiveness be considered. Even the least hint of a fraudulent election and of cutbacks in freedom should be met by turning off the flow of funds.
Just as with debt forgiveness or new loans, foreign aid should be tied to the actuality of political reform and not to its promise. When leaders put themselves at risk of being thrown out by the people, then they show themselves worthy of aid. When leaders allow their books to be audited to detect and publicize corruption, then they are good candidates for aid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their people. Those who refuse to make politics competitive and to expose and correct corruption will just steal aid and should not get it if there is not an overwhelming national security justification for continuing aid.
第九章 战争,和平与世界秩序 Chapter 9 - War, Peace, and World Order
War Fighting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years ago, Sun Tzu literally wrote the book on how to wage war. Although his advice has been influential to leaders down through the centuries, lead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dvisers have contradicted his war-fighting doctrines.
To Try Hard or Not
Remember that large-coalition leaders must keep a broad swath of the people happy. In war that turns out to mean that democrats must care about the people and, of course, soldiers are people. Although conflict involves putting soldiers at risk, democrats do what they can to mitigate such risk. In autocracies, foot soldiers are not politically important. Autocrats do not waste resources protecting them.
Autocrats don’t squander precious resources on the battlefield. And elite well-equipped units are more for crushing domestic opposition than they are fighting a determined foreign foe.
When they need to, democracies try hard. However, often they don’t need to. Indeed they are notorious for being bullies and picking on weaker states, and negotiating whenever they are confronted by a worthy adversary.
Sun Tzu’s advice to his king predicts the behavior of autocrats in World War I: they didn’t make an extraordinary effort to win. The effort by the democratic powers in that same war equally foreshadowed what Caspar Weinberger and so many other American advisers have said to their president:if at first you don’t succeed, try, try again.
When it comes to fighting wars, institutions matter at least as much as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 willingness of democracies to try harder goes a long way to explaining why seemingly weaker democracies often overcome seemingly stronger autocracies.
Fighting for Survival
Autocrats and democrats, at one level, fight over the exact same thing: staying in power. At another level, they are motivated to fight over different things. Democrats more often than autocrats fight when all other means of gaining policy concessions from foreign foes fail. In contrast, autocrats are more likely to fight casually, in the pursuit of land, slaves, and treasure.
Who Survives War
Democrats are much more sensitive to war outcomes than autocrats.
Military success helps democrats retain power while defeat makes removal a near certainty for democrats.
Naturally the common people don’t want war. . . . But, after all, it is the leaders of the country who determine the policy, and it is always a simple matter to drag the people along, whether it is a democracy, or a fascist dictatorship, or a parliament or a communist dictatorship.... All you have to do is tell them they are being attacked, and denounce the pacifists for lack of patriotism and exposing the country to danger. It works the same way in any country.
The US military operates on the principle of no soldier left behind.
The Peace Between Democracies
Democracies hardly ever (some might even say never) fight wars with each other. This is not to say they are peace loving. They are not shy about fighting other states.
Democratic leaders need to deliver policy success or they will be turned out of office. For this reason they only fight wars when they expect to win.
Democracies don’t fight with each other, true. Rather, big democracies pick on little opponents whether they are democratic or not,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they won’t fight back or won’t put up much of a fight. Indeed, that could very well be viewed as a straightforward explanation of the history of democracies engaged in imperial and colonial expansion against weak adversaries with little hope of defending themselves.
Defending the Peace and Nation Building
Unfortunately, actions have not matched the rhetoric. More unfortunately still, the problem lies not in a failure on the presidential level, but with “we, the people.”
In democracies, leaders who fail to deliver the policies their constituents want get deposed. Democrats might say they care about the rights of people overseas to determine their own future, and they might actually care too, but if they want to keep their jobs they will deliver the policies that their people want. Earlier we examined how democrats use foreign aid to buy policy. If that fails, or gets too expensive, then force is always an option. Military victory allows the victors to impose policy.
Democrats remove foreign leaders who are troublesome to them and replace them with puppets. The leaders that rise to the top after an invasion are more often than not handpicked by the victor.
Democratic leaders profess a desire for democratization. Yet the reality is that it is rarely in their interest.
Democratization sounds good in principle only.
The big problem with democratizing overseas continues to lie with we, the people. In most cases we seem to prefer that foreign nations do what we want, not what they want. However, if our interests align then successful democratization is more likely. This is particularly so if there is a rival power that wishes to influence policy.
We have seen that larger coalition systems are extremely selective in their decisions about waging war and smaller coalition systems are not. Democracies only fight when negotiation proves unfruitful and the democrat’s military advantage is overwhelming, or when, without fighting, the democrat’s chances of political survival are slim to none. Furthermore, when war becomes necessary, large-coalition regimes make an extra effort to win if the fight proves difficult. Small-coalition leaders do not if doing so uses up so much treasure that would be better spent on private rewards that keep their cronies loyal. And finally, when a war is over, larger coalition leaders make more effort to enforce the peace and the policy gains they sought through occupation or the imposition of a puppet regime. Small-coalition leaders mostly take the valuable private goods for which they fought and go home, or take over the territory they conquered so as to enjoy the economic fruits of their victory for a long time.
第十章 怎么办?Chapter 10 - What Is To Be Done?
扩大致胜联盟的人数
However,the inherent problem with change is that improving life for one group generally means making at least one other person worse off, and that other person is likely to be a leader if change really will solve the people’s problems. If the individual harmed by change is the ruler or the CEO—the same person who has to initiate the changes in the first place—then we can be confident that change is never going to happen.
Wishful thinking is not a fix and a perfect solution is not our goal and should not be any well-intentioned person’s goal. Even minor improvements in governance can result in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the welfare of potentially millions of people or shareholders.
Rules to Fix By
The group whose desires are most interes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sting betterment is the set of essentials. More often than not, they are the people who can make things happen.
What political insiders want when it comes to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complex, but to understand the reforms they can be expected to support and those they will oppose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ir wants.
So, there are two times when the coalition is most receptive to the urge to improve life for the many, whether those are the people or shareholders: when a leader has just come to power, or when a leader is so old or decrepit that he won’t last much longer. In these circumstances coalition members cannot count on being retained.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an incumbent’s reign the danger of being purged is greatest and so, at these times, coalition members should be most receptive to reform. Effective reform means expanding the coalition and that means that everyone, including the current essentials, has a good chance of being needed by tomorrow’s new leader.
A wise coalition, therefore, works together with the masses to foster an expanded coalition. The people cooperate because it will mean more public goods for them and the coalition cooperates because it will mean reducing the risk of their ending up out on their ear.
What are the lessons here for change? First, coalition members should beware of their susceptibility to purges. Remember that it ticks up when there is a new boss, a dying boss, or a bankrupt boss. At such times, the essential group should begin to press for its own expansion to create the incentives to develop public-spirited policies, democracy, and benefits for all. Purges can still succeed if they can be mounted surreptitiously, so wise coalition members who are not absolutely close to the seat of power would do well to insist on a free press, free speech, and free assembly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unanticipated upheaval. And should they be unlucky enough to be replaced, at least they will have cushioned themselves for a soft landing. Outsiders would be wise to take cues from the same lessons: the time for outside intervention to facilitate democratic change or improved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is when a leader has just come to power or when a leader is near the end of his life.
Lessons from Green Bay
Fixing Democracies
A simple fix that lifts everyone’s longer term welfare is to grandfather in immigrants. Amnesty for illegal immigrants—a dirty word in American political circles—is a mechanism to choose selectively those who demonstrate over a fixed period their ability to help produce revenue by working, paying taxes, and raising children who contribute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national political life, and national social fabric. Give us your poor and let’s see if they can make a better life. Give us your tired and let’s see if they can be energized by participating in making a more public-goods oriented government work better. Give us your huddled masses longing to be free and let’s see if their children don’t grow up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a stronger, more peaceful, and more prosperous society than they first came to. For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the waves of im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have made our winning coalitions bigger and better. They have turned from poor, tired, huddled masses into modern America’s success story. This was no happenstance of time or place. This is the straightforward consequence of easy citizenship and, with it, an expanded winning coalition that makes for better governance.
Removing Misery
iven such circumstances, a smart dictator will look ahead and work out that he is better off liberalizing now than risk being exiled, jailed, or killed later.
Certainly there is little justice in letting former dictators off the hook. But the goal should be to preserve and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many who suffer at the hands of desperate leaders, who might be prepared to step aside in exchange for immunity.
The incentives to encourage leaders to step aside c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if, in exchange for agreeing to step down quickly, they would be granted the right to retain some significant amount of ill-gotten gains, and safe havens for exile where the soon-to-be ex-leadership and their families can live out their lives in peace. Offering such deals might prove self-fulfilling. Once essential supporters believe their leader might take such a deal, they themselves start looking for his replacement, so even if the leader had wanted to stay and fight he might no longer have the support to do so. The urge for retribution is better put aside to give dictators a reason to give up rather than fight.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False Hope
True, meaningful elections might be the final goal, but elections for their own sake should never be the objective.
Ultimately, elections need to follow expanded freedom and not be thought of as presaging it!
Sometimes the problems of the world seem beyond our capacity to solve. Yet there is no mystery about how to eradicate much of the world’s poverty and oppression. People who live with freedom are rarely impoverished and oppressed. Give people the right to say what they want; to write what they want; and to gather to share ideas about what they want, and you are bound to be looking at people whose persons and property are secure and whose lives are content. You are looking at people free to become rich and free to lose their shirts in trying. You are looking at people who are not only materially well off but spiritually and physically, too. Sure, places like Singapore and parts of China prove that it is possible to have a good material life with limited freedom—yet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se are exceptions and not the rule. Economic success can postpone the democratic moment but it ultimately cannot replace it.
A country’s relative share of freedom is ultimately decided by its leaders.
But before we shift blame onto our “flawed” democratic leaders for their failures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we need to remember why it is that they enact the policies that they do. The sworn duty of democratic leaders is to do precisely what we, the people, want.
Our individual concerns about protecting ourselves from unfriendly democracies elsewhere typically trump our longer term belief in the benefits of democracy. Democratic leaders listen to their voters because that is how they and their political party get to keep their jobs. Democratic leaders were elected, after all, to advance the current interests at least of those who chose them. The long run is always on someone else’s watch. Democracy overseas is a great thing for us if, and only if, the people of a democratizing nation happen to want policies that we like. When a foreign people are aligned against our best interest, our best chance of getting what we want is to keep them under the yoke of an oppressor who is willing to do what we, the people, want.
Yes we want people to be free and prosperous, but we don’t want them to be free and prosperous enough to threaten our way of life, our interests, and our well-being—and that is as it should be. That too is a rule to rule by for democratic leaders. They must do what their coalition wants; they are not beholden to the coalition in any other country, just to those who help keep them in power. If we pretend otherwise we will just be engaging in the sort of utopianism that serves as an excuse for not tackling the problems that we can.
We have learned that just about all of political life revolves around the size of the selectorate, the influentials, and the winning coalition. Expand them all, and the interchangeables no more quickly than the coalition, and everything changes for the better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They are liberated to work harder on their own behalf, to become better educated, healthier, wealthier, happier, and free. Their taxes are reduced and their opportunities in life expand dramatically. We can get to these moments of change faster through some of the fixes proposed here but sooner or later every society will cross the divide between small-coalition, large-selectorate misery to a large coalition that is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selectorate—and peace and plenty will ensue. With a little bit of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this can happen everywhere sooner, and if it does we all will prosper from it.
大陆版被删减内容
查询关键词:China、Chinese,英文粗体部分为被河蟹的部分。
英文版P12/190
The second stratum of politics consists of the real selectorate. This is the group that actually chooses the leader. In today’s China (as in the old Soviet Union), it consists of all voting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Saudi Arabia’s monarchy it is the senior 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y; in Great Britain, the voters backing members of parliament from the majority party.
中文版P30:处理方式删除。
英文版P14/190
Strange as it may seem, the same ideas and subtle differences that held true in San Francisco can be applied to illiberal governments like Zimbabwe, China, and Cuba, and even to the more ambiguous sorts of governments like current-day Russia or Venezuela or Singapore.
中文版P37:处理方式删除。
英文版P16/109
For example, a married cou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pays no income tax on the first 32,400 pays no income tax. If their income were, say, 1,000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help support their child. In China, a family with an income of 6,725 in income tax.
中文版P134:处理方式删除。
英文版P48/190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Huang Guangyu, also known as Wong Kwong Ku, fared little better. Starting with nothing but $500 and a street cart, Guangyu created Gome, the largest electrical retailer in China. He was repeatedly ranked as China’s richest individual—until he was sentenced to fourteen years in prison for bribery. It is likely that he was guilty since bribery is commonplace in Chinese business dealings. It is also likely that he and others who have been prosecuted for corruption in China were “chosen for political reasons.”
中文版P135:处理方式整段删除,本段”黄光裕被选择执法”本在“2004年霍尔多科夫斯基”与“在独裁国家,做个富人是不明智的”两段之间。
英文版P58/190
Hobbes was only half right. It is true, as Hobbes’s believed, that happy, well-cared-for people are unlikely to revolt. China’s prolonged economic growth seems to have verified that belief (at least for now). Keep them fat and happy and the masses are unlikely to rise up against you.
中文版P158:处理方式删除
英文版P60/190
Indeed, a common refrain among small-coalition rulers is that the very freedoms, like free speech, free press, and especially freedom of assembly, that promote welfare-improving government policies are luxuries to be doled out only after prosperity is achieved and not before. This seems to be the self-serving claim of leaders who keep their people poor and oppress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poster boy for this view. When Deng Xiaoping introduce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to China in the 1980s, experts in wealthy Western countries contended that now China’s economy would grow and the growth would lead to rapid democratization. Today, more than thirty years into sustained rapid growth we still await these anticipated political reforms. Growth does not guarantee political improvement but neither does it preclude it. The Republic of China (aka Taiw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ka South Korea) are models of building prosperity ahead of democracy. Needless to sa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ertainly is not fond of promoting either of those countries’ experiences.
中文版P163:处理方式删除,删除内容用于列举中国政府宣扬只有经济繁荣之后才考虑民主与自由问题的观点。
英文版P61/190
A far better measure of leaders’ interest in education is the distribution of top universities. With the sole exceptions of China and Singapore, no nondemocratic country has even one university rated among the world’s top 200. Despite its size, and not counting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which were established under British rule before Hong Kong’s return to China in 1997, the best-ranked Chinese university is only in 47th place despite China’s opportunity to draw top minds from its vast population. The highest ranking Russian university, with Russia’s long history of dictatorship, is 210th.
中文版P165:处理方式删除,删除内容说明中国高等教育不怎么样。
英文版P64/190
A smart democrat, of course, tries to avoid such troubles, using eminent domain only when it benefits many people, especially members of the democrat’s constituency (the influentials). It is incredible to see how easily leaders can take people’s proper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ow hard it is to do the same in Hong Kong. When essentials are few, pretty much anything goes.
中文版P178:处理方式删除。
英文版P64/190
Massive construction projects, like the Aswan Dam in Egypt and China’s Three Gorges Dam, are very much like Mobutu’s power grid.
中文版P178:处理方式删除,Three Gorges Dam 即三峡大坝。
英文版P67/190
The comparison of Iran and Chile is far from unusual. China, like Chile, suffered a 7.9 earthquake of its own. It struck in May 2008, bringing down many shoddily constructed schools and apartment buildings, killing nearly 70,000. Even accounting for variations in Chile’s and China’s populations and incomes, it is impossible to reconcil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s death toll and Chile’s, except by reflecting on the incentives to enforce proper building standards in democratic Chile—incentives missing in autocratic China and Iran. And lest it is thought these are special case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democratic Honduras had a 7.1 earthquake in May 2009, with 6 deaths and Italy a 6.3 in April 2009 with 207 deaths.
中文版P184:处理方式删除,内容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导致大量人口死亡。
英文版P80/190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in China mirrored Khrushchev and Gorbachev, but with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All of these leaders seem to have been initially motivated by the sincere desire to improve their economy. All seemed to have recognized that failing to get their economy moving could pose a threat to their hold on power. But unlike Mao, Mikhail, and Nikita, Deng belongs squarely in the hall of fame. Like them, he was not accountable to the people and, like them, he was not hesitant to put down mass movements against his rule. The horrors of Tiananmen Square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But unlike his fellow dictators, he actually had good ideas about how to improve economic performance.
Deng and Singapore’s Lee Kwan Yew are surely among the contemporary world’s two greatest icons of the authoritarian’s hall of fame. They did not sock fortunes away in secret bank accounts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hey did not live the lavish lifestyles of Mobutu Sese Seko or Saddam Hussein. They used their discretionary power over revenue to institute successful,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reforms that made Singaporeans among the world’s wealthiest people and lifted millions of Chinese out of abject poverty.
中文版P228:处理方式第一段整段被张冠李戴删节为一句话“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李光耀确实知道如何改善经济”,实际是讲邓;紧接下来的一段原文邓李并举删节为只讲李一个人。
英文版P95/190
At first, a few especially bold individuals may rise up in revolt. They proclaim their intention to make their country a democracy. Every revolution and every mass movement begins with a promise of democratic reform, of a new government that will lift up the downtrodden and alleviate their suffering. That is an essential ingredient in getting the masses to take to the streets. Of course, it doesn’t always work.
The Chinese communists, for instance, declared the formation of a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on November 7, 1931. They said of their newly declared state,
It is the state of the suppressed workers, farmers, soldiers, and working mass. Its flag calls for the downfall of imperialism, the liquidation of landlords, the overthrow of the warlord government of the Nationalists. We shall establish a soviet government over the whole of China; we shall struggle for the interests of thousands of deprived workers, farmers, and soldiers and other suppressed masses; and to endeavor for peaceful unification of the whole of China.
Jomo Kenyatta, the leader of Kenya’s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its first head of state, likewise declared during a meeting of the Kenya African Union (KAU) on July 26, 1952:
中文版P280:处理方式整段删除,内容是讲毛的革命。
英文版P95/190
Many revolutions end up simply replacing one autocracy with another. On some occasions the successor regime can actually be worse than its predecessor. This might well have been the case with Sergeant Doe’s deposition of Liberia’s True Whig government or Mao’s success against Chiang Kai Shek’s Kuomintang government in China.
中文版P280:处理方式删除,Chiang Kai Shek 即蒋介石。
英文版P100/190
As might be expected, given these facts and the incentives they suggest, instances of 200 or more people dying in earthquakes is much more common in autocracies than democracies.
Not all disasters are equal in the eyes of autocrats. Dictators are particularly wary of natural disasters when they occur in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important centers. Disaster management in China emphasizes this point. When an earthquake struck the remote province of Qinghai in 2010,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response was, at best, halfhearted. In contrast, its handling of disaster relief in the wake of a 2008 earthquake in Sichuan won the approval of much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differences are stark and driven by politics. The Sichuan quake occurred in an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important center where a massed protest could potentially threaten the government. Qinghai is remote and of little political importance. Protest there would do little to threaten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did much less to assist people who could not threaten them.
中文版P280:处理方式整段删除,内容是讲对青海与汶川大地震的不同灾变处理。
英文版P102/190
Common threads run through each of these democratizers—common threads that are absent from revolutions that replaced one dictator with another, such as occurred under Mao Zedong in China, Fidel Castro in Cuba, Porfirio Diaz in Mexico, and Jomo Kenyatta in Kenya.
中文版P301:处理方式删除。
英文版P124/190
Sure, places like Singapore and parts of China prove that it is possible to have a good material life with limited freedom—yet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se are exceptions and not the rule. Economic success can postpone the democratic moment but it ultimately cannot replace it.
中文版P386:处理方式删除。
The Federalist Papers
On the Moral Sentiments
On Democracy in America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自由‧平等‧博愛︰一位法學家對約翰‧密爾的批判
- 前言
- 作者简介
- 内容提要
- 相关单词来源及发展
- 总序(冯克利)
- 译序(冯克利)
- 序(斯圖亞特·D·沃納)
- 編者説明
- 第一版 前言
- 第一章 自由概説
- 第二章 論思想和辯論的自由
- 第三章 論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的區分
- 第四章 自由學説在道德中的應用
- 第五章 平等
- 第六章 博愛
- 第七章 結語
- 附錄一 功利主義筆記
- 附錄二 第二版前言
- 文獻舉要
- 注釋
- 譯後綴語
前言
英文名: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And Three Brief Essays
自由、平等、博爱(法语: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又译为“自由、平等、友爱”、“自由、平等、兄弟”、“自由、平等、团结”。我觉得翻译成自由平等兼爱最好。墨家组织本身就和一神教组织很相像。而根据韩昌黎的《原道》“博爱之谓仁”,而仁显然是爱有等差的,亲亲尊尊之下不可能一视同仁。教友显然比同胞亲,红卫兵举报母亲导致母亲被枪决是再典型不过的案例。
法国大革命本身算是基督教宗教改革的一部分,赖以维系的思想来自于欧陆启蒙运动,而非苏格兰启蒙运动,后者是现代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源泉。而信奉新型自由主义的自由派可以无限划分,源头是马克思主义。
自由只能和机会平等契合,而和结果平等不契合。盲目信奉结果平等,危害巨大。
这里要吐槽一句,译者的中文水平有极大的提升空间,老爱瞎用自己不懂的汉语词汇。。
作者简介
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James Fitziames Stephen,西元1829-1894),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著名法學家,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的伯父。曾在印度工作,生前積極推動英國刑法改革,長期為多家雜誌撰寫評論,對休謨、柏克、吉本、邊沁、托克維爾以及密爾等人的作品也多有臧否。主要著作有《自由·平等·博愛》、《刑法史》、《四季閒暇》等。
内容提要
Students of political theory will welcome the return to print of this brilliant defense of ordered liberty. Impugning John Stuart Mill’s famous treatise, On Liberty, Stephen criticized Mill for turning abstract doctrin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to “the creed of a religion.”
Only the constraints of morality and law make liberty possible, warned Stephen, and attempts to impose unlimited freedom, material equality, and an indiscriminate love of humanity will lead inevitably to coercion and tyranny. Liberty must be restrained by custom and tradition if it is to endure; equality must be limited to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if it is to be just; and fraternity must include actual men, not the amorphous mass of mankind, if it is to be real and genuine.
斯蒂芬以其冷静的目光审视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位一体的价值观。自由作为服务于社会福祉的要素之一,本身只具有工具性价值,因时因地而有利弊。平等和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因各人资质与所处环境不同,自由造成的结果恰恰是最大的不平等。人类因为不可避免的利益之争,及对社会前景与真善美的不同理解,也不可能达致博爱的境地。信言不美,本书论点或许刺耳,所揭示的现实世界图景不甚美好,但也许更接近真实。
在斯蒂芬看来,自由是有秩序的自由,平等是法律之下的平等,而博爱则是一种与自由社会不相容的价值。这种理解正是《自由·平等·博爱》一书最重要的特色,凡是关心自由社会性质的人,显然都应该给予关注。
相关单词来源及发展
西元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指出:“自由即所有人皆拥有的,做一切不伤害其他人的自主权。除了保障社会上其他人享受同样权利外,此天赋的权利不应有任何限制”。“不自由毋宁死”(Vivre libre ou mourir,西元1775年由美国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提出,法国大革命后流行于世,后来成为希腊国家格言)成为共和国的一个重要格言。
平等指所有人视为同等,废弃各人生来和地位的差别,只考虑各人对国家所作出的贡献。1793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西元1795年,平等的定义为“于法律面前,无论受法律保护者,或受法律惩罚者,人人皆平等。平等承认生来的差别,和不受遗传影响的能力。”
西元1795年的法国宪法中,博爱即己所不欲,勿施予人;己所欲者,常施予人的精神。
法国杂志精神的哲学编辑保罗·泰宝说:“我们有多么视自由和平等为权利,也多么有义务以博爱去尊重他人。故此,这是道德的格言。”也有学者认为Fraternité就其本源来看并没有博爱的意思,强调的更多是兄弟关系或类兄弟关系的社群价值。
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及口号。革命爆发时,巴黎镇长让-尼古拉·帕什在巴黎的墙上涂上“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法语: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ou la mort)。首次使用它的政治人物是罗伯斯庇尔,他在西元1790年的国会会议中的演说中,改编了巴什的标语。
高鹏程. 法國大革命並未提出「博愛」口號. 中国: 青海社会科学. 2014: 196–2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30) (中文). 从词根来看,法语中的 Fraternité 的词根是 frāter,它在拉丁文中是 brother 即“兄弟”的意思。在古英文中,brother 这个词写作 brōthor,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作 brōthir,古德文中作 bruoder,希腊语中作 phratē,梵文中作 bhrātar。由此可以判定,Fraternity 起源于 brother 这个词,它在西元14世纪初发展成为副词 brotherly,用来指称类似兄弟关系的群体关系,最后名词化为 Fraternity。
总序(冯克利)
在中国介绍西方保守主义,于今未必是一件能讨好人的事。首先因为它引起的联想不佳。对于深受进步主义观念影响的读者来说,一提起“保守”二字,往往会想到有碍“进步”的旧道统,想到特权和等级秩序,更直白地说,想到抵制变革的“反动势力”。
其次,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对于结构已然相对稳固、运行顺畅的社会来说,或许有很多东西值得保守。但是一个亟待转型的国家,如果好的旧事物留存下来的不多,体制依然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这时人们便更愿意用变革来换取改进。倡导保守者于此不免自作多情,徒言往圣先贤而无“活着的”旧制可以依傍,会因缺乏所谓“建设性”和“前瞻性”而为人所诟病。所以与西方不同,在中国批判激进革命意识形态的人,大多并不以保守主义者自居。
【注:前清不留余地地破坏中国传统社会几乎一切好的内容,“崇祯殡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满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所言非虚!一百年多来,不断激进化的意识形态催生了集古今中外专制思想于一体的利维坦——后清,该统治集团本身就是以西方最极端、最进步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原则的,后清则是不留余地地破坏中国传统社会几乎一切内容(除了同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法家、墨家学说)。被饿死在夹边沟的自由派公知固然活该,但是平民百姓被各种死亡、虐待,这还是很令人“哀民生之多艰”。就目前情况来看,这种危害再过一世也难以消除。后清已再度成为人类公敌,一直在加速,也不知道将来又要用多少人的鲜血来浇灌自由之花了。……为什么要用西方的话术反西方的话术?复辟儒教不行吗?地球上的思想还有比儒学更古老反动的吗?冯克利确实算是大陆学者中为数不多的有一定水平的人,不过他既然是从文化大革命时代过来的人,理解不了中国的文化内核也算正常,不应该苛责老年人。】
这种理解可能没有错,但也忽略了保守主义的另一些特点。
首先,保守主义虽然尚古,但它本身不是古董。……保守主义是与现代世界同步发生的。……保守主义自觉与之对抗的便是“现代性”充满危险的一面,但它本身也是现代思想体系重要的一环。
其次,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保守主义是一种专属于权贵或既得利益的意识形态。其实,保守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在西方便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支持保守主义政治势力的普通民众在欧美遍布各地,可见它并没有特定的阶层归属。厌恶频繁的变化乃人类的天性之一,大变革可以为英雄带来快感,但也能给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严重的不适。多数人并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成为政客施展革新大业的舞台。保守主义所要维护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利益,而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模式。在保守主义看来,这种秩序的存在既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也是文明成长的要件。
【注:保守主义主要保守人类父权制社会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而不断进步的结果便是进步人抛弃人性拥抱兽性,进步分子总会被更进步的人送去投胎!人类天生厌恶频繁的变化(否则无所适从),但也厌恶一切如旧(否则没有新鲜感、激情或动力),微变才是符合人类天性的。微变应该是改革的主体思想。人类厌恶风险,主要是因为不确定性的危机感和至少不会比更差的现状!】
再次,保守主义多被喻为政治列车的刹车器,讽其抱残守缺,不知进取,缺少“行动能力”。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如此。……可见在重新为社会定向的问题上,保守主义思想同样可以提供强大的动力来源。在国际关系领域更不待言,欧美的保守主义者通常比其他政党持更强硬的立场,更加倾向于“行动主义”。
不过,以上所述只涉及保守主义的形式特点。如果观察保守主义的思想内容,则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条理清晰的体系,而是有着十分复杂的成分。则以保守主义鼻祖伯克来说,他向不以理论家自居,其思想缺乏严谨一致的外表,法国的迈斯特与他相比,基督教宿命主义的倾向就要清晰得多。英美保守主义因伯克的缘故而与古典自由主义和法治传统结下不解之缘,同样受伯克影响的德国保守主义,则呈现出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情。在(西元)19世纪,黑格尔是普鲁士国家主义的辩护士,法国的贡斯当和托克维尔则为现代现代商业文明和民主趋势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后的保守主义思想同样成分复杂,有些甚至相互冲突。例如,同为德国文化圈的哈耶克和卡尔·施密特,大概除了可以共享保守主义之名外,两人的思想甚少相似之处。在英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中,奥克肖特的思想很世俗化,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确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其实应该是罗马公教会信徒)。保守主义者在美国通常是小政府和地方主义的支持者,在法国则多是中央集权派。在经济学领域,政治光谱中偏保守的人多为市场至上派,但很多文化保守主义者对经济自由带来的物质主义有很大保留。施特劳斯对现代资本主义嗤之以鼻,可是在安·兰德看来,它是西方文明最珍贵的成果。有些保守主义者常常表现出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倾向,但也有不少保守主义者依然信守由基督教传统中演化出的普世主义。
【注:首先感概一句”贵圈真乱“!结合哈耶克名篇《我为何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冯克利这里的说法显然有点问题。虽然有”大保守“和”小保守“之分,不过作为一个彻底的士人,我的建议就是抛弃整套新话(newspeak)体系,仿效一千年前的理学家一样给儒学理论打上补丁。吾辈应该高举民族、民权、民生这种现代儒学的基础,对洋人文化资源进行适当的取舍,完成”出口转内销“的过程,而不需要全篇用洋人话术来反对另一种洋人话术。由基督教传统中演化出的普世主义给人类文明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这是儒士最应该学习的东西!记住要用魔法打败魔法!】
所有这些难免给人一种印象,保守主义是一个混乱的概念。就如同哈耶克和亨廷顿所说,对于应该保守者为何,保守主义者并无统一的目标。它缺少清晰稳定的政治取向,因此不能提供一种实质性的理想。但是换一个角度看, 思想色彩各不相同的人都愿意用”保守主义“自我或互相标榜,至少说明了它具有强大的工具性价值。保守主义本身可能无力提供一种完备的替代方案,但对于维护社会中某些既有的结构性成分,或避免某些政治方案的恶果,它却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种工具角度来理解保守主义,使它与其他政治学说相比,拥有更多守护原则的实践技艺。所谓”道不自器,与之圆方“,它可以为变革与连续性之间的平衡提供一定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守主义不是政治哲学,而是一种古典意义上的”政策“理论;它不是无视现实的传统主义或者文化原教旨主义,而是现实政治和伦理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保守主义虽然谈不上是一种严整的思想体系,勉强给出清晰的定义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但还是可以为它归纳出一些基本特征。作为一个复杂的思想群体,这些特征不是表现在他们的共同主张上,而更多的是反映在他们的共同反对上。
第一,大体而言,保守主义者对于以现代技术理性为基础的进步主义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进步有无可争议的正面价值,认为眼前的经验并不足以为人的正确行为提供足够信息。无论理念还是技术革新给生活方式造成的改变,其长远后果不是立刻就能看清楚的,所以保守主义者都反对激进变革,对历史和信仰的传统持虔诚的敬畏态度。
【注:激进变革的代表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好学生波尔布特在柬埔寨一系列消灭私有制的实践。】
第二,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社会不是外在于人类活动的客观事实,可以由人对其任意加以改造。社会最可贵之处,是通过特定群体长时间的实践活动而形成的内生秩序,它类似于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其最好的、最自然的变化是演化与生长,这个过程不排除理性的作用,但由于人性天生并不完美,所以理性在引领变革中最重要的作用是审慎。
第三,社会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家庭伦理、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来维系,它们使人们在生活中感到惬意,形成真正的权威认同。如果这些因素受到破坏,恢复起来将极为困难。因此,培育和守护这些因素,乃是维持社会健康的必要条件。
第四,保守主义者对政府权力一向保持戒备,不信任基于权利平等的现代民主政体具有至上价值。他们认为贤能政治(meritcracy)更有益于社会整合和道德风气的培养;肯定基于自然原因的不平等的正面意义。
【注:扎心了,民主小清新~突然意识到,欧美之所以常用民主专制划分方式给国家分类而不是国人熟悉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划分方式,当然是因为嗓门大的它们(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也反对资本主义。】
第五,保守主义还有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特点:它严重依靠历史和传统叙事,认为所谓科学思维提供的各种原理不具有道德和社会优势,因此排斥超越时空的理性批判。这使保守主义文献在话语风格上文学叙述多于逻辑分析,引经据典和释义成分多于体系建构,这也是保守主义缺乏系统性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译序(冯克利)
一
借用韦伯的话说,这当然是一种”卡利斯玛“式崇拜现象的一部分。由此形成的精神环境,也有着帕累托所言”狮子型精英“那种讲原则、出手狠的特点。在这种风气的熏陶下,不少文化人每每要争当伟大理念之代言。无论得失成败,对立的两造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染上了”先知“和”圣徒“意识。由于肤浅的”进步观念“作祟,他们”怀着对真理的热情,死死抓住幻觉“,用”忤逆人类进步潮流“相互指责。
掌握了内在进步规律的人,会有通神的感觉,视一切陈规陋习如糟糠,此时他是神还是兽,往往是分不清楚的。在高度原则化、理念化的思想气氛中,他很容易把辩论的政治变成肉体的政治。即使血光之灾过去,观念体系所形成的价值和利益刚性,也使政治话语中充满禁忌。或有表面的安定,其下却四处预埋了冲突的伏笔。这段以进步主义作为主旋律的思想史,一度表现得意气风发,自信十足,但是回头想一想,它的场面热闹归热闹,留给后人的感概,或许远远多过成就。
【注:左衽的通病便是如此。】
二
列文森在《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曾把近世英国的上层官员比作中国古典社会沉迷于诗画的士大夫,他们都是人文世界的饱学之士,对于专攻一技一科唯恐避之不及,而是把古典教育作为不可缺少的素养,以为培养和牵引政治志向之用。前有伯克、麦考利和迪斯雷利,后有丘吉尔,都可作为这类人物的杰出代表。不言而喻,这种看重古典人文修养的风气,与现代社会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化的要求,是大异其趣的。
【注:英美这套体制确实比较符合儒家理念。】
斯蒂芬便是这样一位抗拒现代官僚理性化和技术化趋势的法律人。正如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所说,即使把他的法律技能与实务统统拿掉,留下的仍是一个出色的文人。他虽然未像伯克那样,弃法律而去趟政党政治那一潭浑水,却没有韦伯所说的手艺人毛病。他在自己的行当里干得有声有色,所著《英国刑法史》曾令梅特兰击节叹赏:”我每次拿起这本书,总被他的研究的彻底性和判断的公正性所打动。“而且他还是当时闻名英伦的政论家,他曾为多家著名杂志撰写时政和思想评论,行文丝毫不带匠气,处处显露出诗学、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造诣,对于诸多思想巨擘如霍布斯、休谟、吉本、伯克、边沁和托克维尔等,都有相当细致的评说。
不过,撇开法学著述不论,斯蒂芬的文字中最为知名者,当非这本《自由平等博爱》莫属。就像白哲浩的《英国宪制》一样,该书先是在(西元)1872年连载于《蓓尔美街报》(Pall Mall Gazette),次年便出了单行本。编者瓦纳(Stuart D. Warner)在概括书中的思想时,把斯蒂芬成为”英国古老自由制度的捍卫者“,因为在他看来,一些新的谬说正威胁着这种制度,其集中体现便是密尔的《论自由》、《论妇女的屈从地位》和《功利主义》这些风行一时的著作。瓦纳继而指出,斯蒂芬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破坏者,他在抨击密尔时,也系统阐述了自己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解,即”自由是有秩序的自由,平等是法律之下的平等,而博爱则是一种与自由社会不相容的价值,这是《自由·平等·博爱》一书最重要的特色“。这种概括相当简洁有力,但未免有教条化之失。
如前所说,斯蒂芬并非一个技术型的法律人,他对”自由、平等、博爱“这个”三位一体口号“的思考,广泛涉及道德信仰和哲学层面。作为一名法律人,他的演说当然不会完全脱去法律的眼光。按此,英国百姓享有的自由是经过漫长的法律实务而形成,而不像欧陆那样更多地通过政治哲学的途径传播。但在阅读斯蒂芬时尤须记住几点。以政治思想的基调而论,他是霍布斯的传人,甚至权威和信仰体系对维系社会的重要作用。此外,该书的构思与写作是发生于他在英印当局服官期间,作为一个身处异邦,学养极佳的英国人,他在思考流行于欧洲的价值观念时,可以很方便地参照近在身边地另一种异域文化,这为他质疑那些那些形而上政治口号的普世性提供了强大的经验资源。其三,正如他在该书的前言中所说,彼时欧洲思想界已经变得:”十分荒谬和贫乏,就像1870至1871年我在印度政府总部读过的欧洲报纸一样“。
三
……由斯蒂芬设为抨击靶心的约翰·密尔著作的流行,我i们便可看到”自由、平等、博爱“已经变为这种政治游戏中进行动员的”大词“,俨然获得了今人所谓”普世价值“的力量。不消说,口号的作用往往大于它的真实含义,成为”荒谬和贫乏“的迷魂药。
但是,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不仅仅是口号,还有许多对传统自由派来说十分陌生的新因素。例如现代福利主义(即密尔式”新功利主义“)的出现,自由的内涵开始向社会平等和集体选择一端倾斜,以及科技和生产力引起的对普遍改善人类境况的乐观展望。
法律人的优点(或是缺点,端看你采取何种立场)之一,但是他既不相信口号,也不相信群众。斯蒂芬告诫后人,”把各种光辉灿烂的前景呈现于人类集体面前“,仿佛只要废除人类行为的一切限制,”承认全人类实质性的平等,奉行博爱或普世之爱,就能发现通过这些前景的道路“。密尔有一条著名的自由原则:”人类被允许一个人或集体的方式对其任何成员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自我防卫;对文明社会的任何一个成员,可以不顾他的意志对他正当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阻止他伤害别人。“而在斯蒂芬看来,人类复杂的处境使这条原则无法适用。仅仅以”自卫“作为强制的理由,无异于取消大多数限制,而它们是维系社会不可或缺的。
这种认识显然来自斯蒂芬对人的悲观看法,……。在他眼中,无论采用何种善恶说,总是有大量无所用心、自私自利、感情用事、轻率懒惰的人。”在鼓吹自由平等时,你必须先想清楚他们占多大比例,再考虑言论自由能把他们提高多少。“像当年的许多保守派一样,他也隐约感到由这些人组成的”群众社会“正在来临,并对此充满警觉。针对把平等作为主要诉求、已经颇成气象的社会主义运动,他早在其变为制度现实的半个世纪以前就断言:若让人人享有物质平等,把劳动成果集中起来养活社会,“你确实为平等和博爱赋予了十分明确的含义,但这必须绝对地排斥自由。经验证明,这不仅是个理论难题,也是个实践难题,是一切社会主义方案无法克服的障碍,它解释了它们的失败。”
既然对群众有此看法,精英主义言论也就不足为怪了。斯蒂芬虽然无缘看到稍后出现的更加雄辩的精英论,却是生活在一个把精英的存在作为事实而不是问题的传统之中。他先于莫斯卡和帕累托提出了精英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使把普选定为法律,你离平等仍会如同过去一样遥远;权力形式变了,其实质却未变,伟大的军人品质会使一个人成为军政统治者,君主政体下国王所看重的品质将会给人带来权力,而在纯粹的民主政体中,统治者将是那些操纵选民的人及其朋党,但“他们与选民之间的平等,不会大于君主政体下的军人或大臣与臣民之间的平等”。
不难看出,斯蒂芬的精英论是源自这一类人皆有的“求实精神”,这也是他敢于向彼时名声盖世的密尔发起挑战的主要动力。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他针锋相对地列出了三个严苛的观察:(1)总是存在着人们不可以享有自由的大量事情;(2)他们从根本上说是不平等的;(3)他们根本不是情同手足的兄弟。
既然“自由、平等、博爱”皆不能得到这些现实观察的支持,政治论说也就不能以此为基础。相反,最令人畏惧的强制——战争,才是“为各民族提供生存基础的原则”,“它决定着民族是否生存以及如何生存;决定着……他们的宗教、法律、道德形式和全部生活格调”;战争不仅是君主的“最后手段”,也是任何人类社会的最后手段,它划定了特定时空中个人自由的范围。斯蒂芬用马基雅维利式的语言,把自己的观点概括为一句话:权力先于自由,从本质上说自由依赖于权力;只有在明智而强大的政府之下自由才能存在。 因此,对基督教敬畏有加的斯蒂芬,并不认为当年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罗马总督彼拉多有何过错:这是奉行责任伦理必然得出的结论。在他看来,总督的“首要责任是维护巴勒斯坦的和平”,即使违反米尔的自由原则,他也必须为决断承担风险。因此斯蒂芬喜欢用寓言的笔法,拿水流和疏浚工程来比喻自由与权力的关系:……
这是提醒人们,自然状态下的自由是毫无意义的,自由的价值来自于它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发挥的作用。斯蒂芬用他在印度的经历告诉读者,为自由提供权利和约束、赋予它以实际内容的善观念,在不同时代和地区是大不相同的。基督徒的理想有别于古罗马,穆斯林或印度教徒几乎下意识地认为法律和宗教是一回事。“使人类结合在一起的内心深处的同情和无数纽带,是他们各具特色的性格和观念“,这会“在他们之间产生、并且必定永远产生持续不断的冲突,……他们之间存在着真正的、本质的、永恒的冲突”。这仿佛是对尼采“爱之火与憎之火在一切道德之名中燃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回应,而斯蒂芬也确实跟尼采一样,已然置身于一个价值分裂的社会,阿克顿所说的那个“稳定、持续、自发的世界”已一去不返,普世的启蒙精神也己丧失了自信。
【注:英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儒家追求确实比较相像!今日全中国的公知仍不知从传统中汲取力量而是一昧地在启蒙,多挨点铁拳也不可能有什么改观,哎!】
四
但是,如果只把斯蒂芬视为一个霍布斯主义者,那就大错特错了。作为一个法律人,他反而与霍布斯大力抨击的爱德华·库克(Edward Coke)大法官更为相似。与坚持“政治之本来面目”的很多人不同,斯蒂芬的现实主义并未使他从这种冲突中得出“强权政治”(Machtpolitik)的结论;他也没有像尼采那样,把“热爱和平只作为新战争的手段”。在冷酷的现实眼光之外,他有自己的政治理念,那是一种更开明的“治理技艺”。
一方面,他并不像那些主张政教分离的人,认为可以把宗教做非政治化的处理悬置于一边。道德对政治行为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它像“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约翰福音》)。既然由道德形成的自由观因地因人而异,密尔的普世自由原则与一地法律所要保护的自由便是不相干的。由法律划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要想做到普遍有益,就要“公正反映社会的道德现状”,适应享有这些权利、遵守这些义务的人。法律的威信不是来自形而上的推理,而是来自它所服务的社会的善观念。
斯蒂芬由此提出了他的立法原则:在任何情况下,立法都要适应一国当时的道德水准。如果社会没有毫不含糊地普遍谴责某事,那么你不可能对它进行惩罚,不然必会“引起严重的虚伪和公愤”。公正的法律惩罚必须取得在道德上占压倒优势的多数的支持,因为“法律不可能比它的民族更优秀,尽管它能够随着标准的提升而日趋严谨”。
【注:孟子有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斯蒂芬的话或可作为我们先贤的一条正解。】
基于这种道德和法治观,斯蒂芬在看待各种价值观的分歧时,便与“强权政治”分道扬镳了。他说,虽然利害关系和对立观念使人类免不了各种冲突,但“人生的伟大技艺”不在于力求一方获胜,而在于对它们加以控制,“不要夸大各自目标的价值”,以使人们尽可能少受冲突的伤害。这可以让我们想到西塞罗在《论责任》中的那段名言:“具有高超的政治才干和十分明智的头脑的好公民所应当做的,不是把公民之间的利益对立起来,而是把这些人的利益在平等公正的原则基础上统一起来。”此外,有无数的差异显然也能增加人生的乐趣,如果“人人都像鲱鱼一样”,生活反而变得单调乏味。更有大量的差异和冲突,与其说存在于善恶之间,不如说存在于“善的不同形式之间”,是“好人与好人之间的对抗”。就如同恶与恶之间也有冲突一样,是故西谚有云:与恶魔对抗时,当心自己也变成恶魔。
斯蒂芬所谓善与善之间也会发生冲突,该如何理解呢?举例来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或人们常提出的问题:“母亲与老婆双双落水,你当先救哪一个?”再如“其父攘羊”故事中的忠孝冲突,这些都是善善相争的场景,在今天的学术语言中,我们更多地把它称为“价值排序”。鱼和熊掌,母亲和老婆,忠与孝,皆“善之属”也,但对于它们的权衡或取舍却会产生严重的对立。如果这种排序的分歧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会造成严重心理分裂;如果是两人或众人的排序不同,则必会带来思想甚至行为的冲突,没有事先确定的规则,不管它会给人生带来多少不便或遗憾,亦不管它在哲学层面多么难以解决,这类冲突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是“实践规则”,无力解决理念的对错,只为减轻不可避免的冲突。
斯蒂芬告诉我们,在这种尚无确定的规则加以解决的价值冲突面前,你当以平和的心态检验自己的力量和技巧,而不应把对手视为你死我活的关系。用他的话说,“卑鄙懦弱的可靠标志,就是不以公正、友善的态度对待对手,缺乏欣然接受公平的失败的决心”,而“足以弥补许多恶行的美德”,便是在斗争中尽职尽责全力取胜,失败后坦然接受结果。当然,唯有独立而公平的法则,才能为这种“公平的”胜败提供保障。
其次,斯蒂芬基于他对这种“善善之间”、“好人之间”的冲突的认识,得出了他的平衡治理的思想。在他看来,英国拥有良好的政制,“既因为有保守,也因为有怀疑”。自(西元)17世纪以降,清教徒和辉格党固然取得了比保王党、托利党和保守派更多的成功,“但社会现状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并非单独哪一方的功劳。政治问题上的“一切谬论之母”是,“几乎每个作者都只宣扬众多因素中的一个”,而健全的态度则应当是“按照我国的风俗参与战斗,做一个讲风度,骨子里相互友好的男子汉”。考虑到本文开头所说的思想失衡的状况,这些话是颇值得玩味再三的。
斯蒂芬是吉本的热心读者。作者犹记得,被吉本推崇备至的罗马大史家波里比阿,从对命运的反思中知晓了所有的民族、城市和权威都必然衰亡,他把西庇阿有关迦太基败亡的话——常胜的罗马有朝一日也要遭受同样的命运——作为最具政治眼光、最深刻的表述,洛维特则把这种胜利之时想到命运可能突然改变的智慧,视为政治家最伟大的品质。至少就这种历史观而言,说保守主义缺少前瞻性是浅薄的。斯蒂芬正是继承了这种古老的命运观,深知在面对吉凶难测的命运时,逻辑、分析甚至经验都无法帮助我们,“只有适当的谨慎才会使我们有正确的作为”。他说,人们出于各种原因给行为分出善恶,并用劝诫和强制手段去惩善扬恶,但善恶判断是经常出错的;人类的动机固然皆出于利己,但同样真实的是,在我们的思想、感情和言行中,爱恨情仇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切不可“为我们所看重的事情附上不着边际的价值”。通晓国故者不难看出,这与“天下之事,有善有恶,……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唯见其善。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爱憎之间,所宜详慎”(魏征《谏太宗十思书》),本是奥义相通的。
人性的演出就像自然史一样,既有美妙的节律,又时常表现得残酷无情。从既往通向未来的人类史,也像一座让人既好奇又困惑的迷宫。在这座迷宫里,正如老子所言,“祸莫大于无敌”,自鸣得意的顺畅旅程,往往意味着在失败之路上走得更远。所以我们无法把这个常令人悲哀的世界仅仅作为一个事实,而是必须做出价值判断和选择。
不消说,这些话仍是“现实政治”(Realpolitik),但与飞扬跋扈的“强权政治”(Machtpolitik)已经大相径庭。无独有偶,就在斯蒂芬写下这段话的五十年后,价值混乱已是欧洲人的生活常态,技术进步不过是“扩大了心灵流浪的半径”,彼时晚年的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也说过一段类似的话:“政治是一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斯蒂芬和韦伯的这些言论,显然属于“责任伦理”的范畴,也是斯蒂芬抨击密尔普世主义自由观的重要原由之一,虽然他这本书里的很多内容,尤其对密尔的一些指摘,只有用“谬论中潜藏真理,真理亦有其弱点”的眼光,才能理解其价值所在。好在这于政治学说乃是常见之事。平心而论,斯蒂芬并非不赞成自由制度,而是对它在复杂现实中的操作难度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在判断民主与平等的趋势上是失败的,他没有托克维尔那样的眼光,既深知民主和平等之弊,也看到了它更加“符合人性”,从而预见到它将决定未来世界的政治格局。但是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混乱及其为意识形态动员提供的可怕机会,斯蒂芬却表现出过人的警觉。与之相比,托克维尔担心社会的同质化,显然是错误的,这是托克维尔所不及的。无论他的思想属于什么主义,表现出多少内在紧张与不连贯,他对制度容纳价值冲突能力的担忧及其相应的治理之道是充满智慧的。这种基于平衡感和责任意识的政治观,至少于作者而言,是既很感人,也很健全的。
【注:美国迄今也不算是个民主国家。如果美国真变成个一人一票的民主国家的话,我们中国人有喜有忧,具体怎么样全看吾辈作为了!】
五
最后,还需就翻译问题聊缀数语,不为开脱,而在提醒有志于研习西学的同好,借助于翻译文献了解西学,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弊,入木三分是绝对谈不上的。翻译近乎篡改,这已是译界的常识,盖文字转换之间流失的东西,往往正是一种特定文化生命历程的精髓。兹姑举两例,一庄一谐。
Liberty(自由)是今天我们时时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自由政制固然是近世的产物,但“自由”这个概念并非近代的发明,而是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它体内流淌的血液中,掺杂着希腊语elcutheria和拉丁语libertas的基因。贡斯当把前者视为现代暴政的来源之一,梅因则对后者赞赏有加。《约翰福音》中“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si ergo Filius vos liberaverit vere liberi eritis.)又为其注入了信仰和良知的力量,有人以为这是自由的真正价值之所在,有人却觉得这为这为现代社会增加了多余的精神负担。
若把这些术语统统译为“自由”两字,它们之间细微的语义差别与关联是难以辨析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也有一段对英国自由传统十分精彩的论说,他称“英国法一直是用野蛮的封建语言来表达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正是英国的法,把古代日耳曼自由的精华,即个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不受任何干涉(法庭的干涉除外)的独立性的精华,保存了好几个世纪,并把它们移植到美洲和各殖民地。这些东西在大陆上专制君主时期已经消失,至今在任何地方都未能完全恢复”。对于恩格斯这里所说的“自由”,如果不知它在封建时代常以“liberties”的复数形式出现,是可以在领主或教会法庭上操作的东西(所以恩格斯才特别提到“法庭的干涉除外”),而不是现代人在广场上高喊的“Liberty!”也就难以理解“野蛮的封建语言”何以表达“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或斯塔尔夫人为何说“自由是古典的,专制是现代的”。须知,此一“古典的自由”,并非指李白诗句“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那种中国式的“古典自由”,对此,我们最好还是把它理解为“逍遥”。这也正如韦伯笔下的“imperium”,它既不同于power,也有异于authority,若把它简单译为“权力”或“治权”,汉语读者便绝无可能知道这种称为“imperium”的权力形态的出现,标志着“正当性命令”与“正当性规范”有了区分,通晓政治史的人都知道,此一分野的形成,乃是促成现代政治自由制度化的要素之一。
再说俗的一例。甲鱼现在是我们餐桌上一道常见的佳肴,可是在西班牙语中,甲鱼和乌龟是不分的,都叫做“tortuga”,而这个tortuga已被收入濒临灭绝动物名录,受到政府的A级保护,无论捕杀食用,概在禁止之列。几年前,马德里一家中餐馆被人举报到警局,说它每天都在用tortuga款待食客。警察一听,这还了得,旋即派员搜查传讯,然后以杀害和出售受保护动物的罪名把餐馆老板告上公堂。西班牙各大媒体也闻风而动,《国家报》和《世界报》都以中餐馆用濒危动物大发横财为名进行炒作。餐馆老板赶紧找来辩护人解释说,俺这个tortuga是中国的tortuga,不是你们西班牙人说的tortuga;俺这是从中国运来的人工养殖的水产品,与你们保护动物名录上的tortuga完全不搭界。可是西班牙警察却不听这一套,法律就是法律,tortuga就是tortuga,岂能管你是从哪里搞来的?结果餐馆老板有口莫辩,不得不等待可能长达三年以上的诉讼过程,因为此案的审理需要先研究tortuga的拉丁语词源和动物分类中种属纲目的关系。在没有搞清楚保护动物名录上的tortuga是否包括水产口甲鱼之前,他那道tortuga汤的佳肴,也只好先从餐馆菜单上抹掉了。
这件由语言差异造成的尴尬事,或可作为海德格尔“语言乃存在的家园”的一个生动签注。海氏的学问深奥得不得了,满篇都是对现代技术世界里如何重构生命价值的终极究问。中土大多数人的实存主义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境界,只是标举“敬鬼神而远之”和“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为人生鹄的。有一点儿价值关切的人,顶多再加上一句“割不正不食”。但由此两端可见,人生之祸福,系于语言符号者大矣,无论事关精神和制度层面的自由,还是甲鱼汤带来的口福之乐。我们用来表达观念名物的各种词语,并非通行于天下、世代不易的数学符号,它们所包含的意义亦非我们自己所创,而是数千年人类各种选择行为不断积淀的结果。是故语言分析学派所谓的词义约定说,在今天很多人看来已成笑柄。离开各种称谓的文化背景、发生史和成长史,便不可能理解一种价值在另一种文化中的移植与生根何以如此艰难,对此,西班牙那个中餐馆的老板,大概与我们这些整天浸淫于“崇高观念”中的人,有着同样切身的感受。
其实,对于价值的存在有赖于正名,我们的先贤亦多有深刻的见地,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是也。清代大儒戴震亦有言:“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此段话正可与上述西方自由词义的流变过程相互印证,很好地点明了价值意蕴(“道”)对符号(“字”和“词”)的高依存度,而这是只有借助于诂词训字的功夫才能领会的。
唠唠叨叨讲了这许多,想要表达的意思说来也简单:研读西学,尤其是各门人文学科,需要调动自己心灵的力量,对符号中的精神世界进行狄尔泰所谓的“理解”(Verstehen)与“阐释”(Auslegung)(不消说,这也是两个一经译者插手便神髓顿失的概念),这跟阅读翻译过来的汽车驾驶手册是大不相同的。所以我以为,为使这种“理解”与“阐释”的过程更为通透,人文的阅读,最好还是以原典为主,译本为辅,不如此便难得其堂奥。这本《自由·平等·博爱》的译稿,便是我的学生杨日鹏在我敦促下阅读与理解西学原著的副产品。全书先由他在精读基础上初译一遍,然后再经我反复润色加工,其间不时穿插着师生二人有关概念解释与译名推敲的讨论,留下了一段愉快的治学经历。
当然,无论我们做出多少努力,借用上面中餐馆事例的寓意,这个中译本也只能算是强以乌龟作鳖用,无论烹饪手法多高明,龟汤跟甲鱼汤毕竟不是一个味道。它充其量只能为无暇看或尚不能看英文著作的读者,提供一个初识斯蒂芬先生的途径。虽有字斟句酌的辛苦,作者文本的原意能得其八九成,已属万幸,断不敢有达诂的妄想。再者,即使有这八九成的收获,译者困于学识之不逮,也难免留有错讹纰漏,这是期期然有待于各路方家赐教的。
序(斯圖亞特·D·沃納)
斯蒂芬以英国古老自由制度的捍卫者自居,指出了一些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这些错误观点还仍然在引领风气。为了匡正这些错误,他撰写了《自由・平等・博爱》一书。他发现,在约翰·密尔的三本著作中,这些观点得到了最充分有力的阐述,它们分别是《论自由》、《论妇女的屈从地位》和《功利主义》。因此,斯蒂芬在《自由·平等·博爱》一书中严词批驳了密尔的政治哲学。不过,斯蒂芬不只是批驳者,通观《自由·平等·博爱》全书,我们可以看到,斯蒂芬本人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解,是和对密尔的批评交织在一起的。**在斯蒂芬看来,自由是秩序之下的自由,平等是法律之下的平等,而博爱则是一种与自由社会不相容的价值。 **这种理解正是《自由·平等·博爱》一书最重要的特色,凡是关心自由社会性质的人,显然都应该给予关注。
斯蒂芬在思想上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但是他对道德、社会和政治事务的理解,也许大多归功于边沁和霍布斯。
边沁使斯蒂芬喜欢上了功利主义。但斯蒂芬的功利主义不是边沁或亨利·西季威克的《伦理学方法》所阐述的那种技术和哲学教条,而是一种把观察和事实置于抽象推理之上的精神取向。斯蒂芬的功利主义最显著的标志是,他认为对道德和政治生活进行冷静理智的评价,需要搞清楚采取这种而非那种行动的利弊。评价我们道德和政治生活的起点,要求我们从自己的处境——我们的时代、地点和环境——入手,因为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接下来要做什么,只有先搞清楚我们当下的处境,才能给予解答。所以,斯蒂芬的功利主义是以改良而不是取消当前的实践为宗旨。不言而喻,这不是那种整齐划一的道德和政治观。
霍布斯对斯蒂芬有着更广泛因为大概也是更大的影响。斯蒂芬十分推崇霍布斯,把他成为“最伟大的英国哲学家”。斯蒂芬在谈到《利维坦》时写到:“几乎没有任何一本思想巨著有如此厚重的分量、如此透彻全面的思考,如此深思熟虑,字字句句都反映着作者的整体思想。”贯穿于《利维坦》全书的一个观点,尤其吸引着斯蒂芬的注意,那就是政治哲学要依赖于一种人性观。故也难怪,斯蒂芬本人的人性观为《自由·平等·博爱》注入了活力,它引导我们把斯蒂芬的著作看作对适合于政治社会这个实践世界的人性的思考。
对斯蒂芬影响最大的是霍布斯的精神,而不是他的哪一种具体理论,但霍布斯思想的两个显著特征,却深深渗透于斯蒂芬的作品之中。其中之一是这样一种观点:人类的利益相互冲突,此乃人类处境不可改变的特征;因为个人利益有冲突,所以他们会形成不同的“善”的观念。
霍布斯思想中对斯蒂芬影响甚大的第二个特征,是社会秩序有赖于使用强制力量的观点。按这种观点,社会秩序需要道德、法律和宗教的限制;这些限制形式从某种人类行为的协调作用中获得了形成社会秩序的权力。
【注:自由是有边界的,而这个边界需要公权力来维系,公权力的范围则由道德、法律、风俗来确定。】
在《自由・平等・博爱》一书中,斯蒂芬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同时他也着力表明,他并非他本人所说的“奴隶制、等级制和仇恨”的捍卫者。但是他深信,“自由、平等、博爱”信条的许多阐释者,夸大了这个著名的三位一体价值观所设想的政治安排的优点,忽视了它的弊端,从而歪曲了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正确理解。
斯蒂芬在《自由·平等·博爱》中着重揭示了这些弊端。现在我们就来谈谈他的理解。
▐ 自由是秩序之下的自由
斯蒂芬的自由观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斯蒂芬把自由视为一种工具性价值,它本身不具有内在价值,作为自由之首要服务对象的终极价值是社会福祉。……不把自由当作目的本身,并不是轻视自由,或是抹杀它在文明世界发挥的核心作用。正如斯蒂芬所说,这不如说是承认自由像人类生活的其他一切社会要素一样,也有着自身的利弊;如果我们最关心的是社会福祉,那么在任何既定的自由弊大于利的环境下,我们就不应当盲目地支持这种自由。
斯蒂芬自由观的第二个特征是,自由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斯蒂芬将不存在限制的状态理解为自由的核心;然而,自由又不能被理解为不存在任何限制。跟霍布斯一样,斯蒂芬认为,没有任何限制,根本就不可能有社会,从而也不可能有自由的存在。若想让社会存在,限制是必不可少的,即使这仅仅是因为人类的状况是有些人的行为与另一些人的行为必然经常发生冲突。对社会限制作用的这种理解,是斯蒂芬区分自由和许可的基础,并且促使他将自由理解为“不存在有害的限制”。根据这种自由观,道德、法律和宗教信仰被视为对个人行为的限制,但它们是无害的,所以不构成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事实上,从最深层的意义上说,正是这些限制使行为的自由成为可能。这些限制构成了一个权力领域,故斯蒂芬能够断言:“自由从本质上说依赖于权力……”
现在我们明白了,斯蒂芬为何经常借用输水管道工程来阐明自由的本质。水管管口的性质和价值,是由制约着它的事物的性质赋予的,同理,自由的性质和价值也有赖于那些制约着它从而形成它的事物,即道德、宗教和法律。可见,社会的各项自由,是由提供了选择之可能性的各种限制构成的。因此斯蒂芬认为,在道德、法律和宗教限制的背景之外谈论自由毫无意义。
【注:用中国古话来说,freedom就是无所御,没有凭借就没有限制,但生活中又不能真的无所御,于是这种思想只能是思想上的“逍遥”。】
斯蒂芬促使人们去理解“有序的自由”或“道德和法律之下的自由”。自由的部分价值在于,它允许个人做出自己的选择,或者更确切地说,做出这一组选择而不是另一组选择,因为这有益于社会福祉。重要的是,某些选择必须被禁止。对人类而言,只有在道德、政治、法律和宗教制度构成的限制体系内,才有做出真正选择的可能;这些制度形成了种种社会安排,它使个人能够追求与其他人相互协调的自己的目标。因此,按斯蒂芬的分析,自由的性质和价值存在于规范自由的限制之中:没有限制,就没有自由。
在塑造一般社会尤其是自由社会的限制当中,道德是最重要的。斯蒂芬认为,道德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人们害怕别人的指责和看法、害怕受到排斥构成的。所以斯蒂芬说:“以厌恶的态度看待某些行为的习俗,乃是道德的本质。”按斯蒂芬的理解,这种厌恶或非议具有强制性。根据这种解释,把道德视为一个暴力系统亦未尝不可,但这种暴力是他人施加的压力,而不是政府施加的惩罚(或以惩罚相威胁)。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观点是,按斯蒂芬的理解,在建立塑造自由并使其具有价值的限制体系方法,道德施加的限制,在其广泛性和重要性上,要大大超过法律的限制:
刑法本身可以被看作禁止的手段,它与耶和华批准的道德观和道德形式相比并不更加重要。一个人的某种行为因惧怕当地的法律而受到限制,却有许多人的不计其数的行为因惧于四邻的非议而受到限制,这就是道德的惩罚;或因担心来世受罚而受到限制,这就是信仰的惩罚;或害怕内心的不安而受到限制,这也许可以称为良心的惩罚。
【注:道德本质上是维系民族共同体延续的社会规范,凡是不利于共同体延续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而在五胡乱华时期猛猛杀五胡或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坑蒙拐骗”日本鬼子都是符合道德的,毕竟这些行为有助于我们民族和文明延续。】
斯蒂芬对人类状况的认识,深刻影响着他对道德的认识,即把道德看作一个塑造个人行为的限制体系。斯蒂芬摒弃对人类盲目乐观的理解,持有一种在有些人看来——也许不无理由——悲观暗淡的立场。也许更为准确的看法是,斯蒂芬提供了一种对人类的冷静理解,一种把握了人类状况之祸福的理解。没有道德施加的自律,个人会倾向于过一种游手好闲、了无生趣的生活,既没有高雅的教养,也缺少追求伟大人格的动力。斯蒂芬认为,人类的状况并不是一个仅有伟大人格或卑劣人格组成的世界,它要比这暧昧得多:我们是一个混合体。人类的灵魂一般而言志趣不高,这委实不幸;然而,斯蒂芬认为,人类确实有社会欲望,它与道德限制结合在一起,有助于维持一种社会秩序,它使伟大的人格和自由成为可能并蒸蒸日上。斯蒂芬虽然摒弃对人类的乐观看法,但也热心呵护着少数人能够培养出的英国高雅文化。不过,不论是能够具备高雅文化的少数,还是尚未尊奉奥古斯丁或加尔文教义种大为受益的人,都脱不了自律和他律的道德。
斯蒂芬认为自由只有工具性的价值,因此不难理解,他为何摒弃一切绝对简单的自由原则,即具体指明哪些自由应予保护、应当在何时何地受到保护的原则。 斯蒂芬写道:“我们必须以更加谨慎的方式,只限于评论经验显示给我们的事情,即在特定情况下自由和强制各自具有哪些利弊。”不过,有一些自由,是斯蒂芬在《自由·平等·博爱》等著作中一贯重视的,他相信这些自由对于文明生活至关重要。首先是财产权:“在各项自由之中,最重要、得到最普遍承认的自由,莫过于获得财产的自由。”大概会令人诧异的是,在斯蒂芬看来,第二项极为重要的自由是隐私权:“在任何情况下,立法和舆论都应一丝不苟地尊重隐私……试图用法律或舆论的强制去调整家庭内部事务、爱情或友情关系,或其他许多同类事务,就像试图用钳子从眼球上夹出人的睫毛一样,这会把眼球拽出来,但绝对得不到睫毛。”
【注:极权主义民主往往都是大锅饭形式的,往往以公有制来控制所有或大部分的财产,并以此来培养党羽镇压异己维持极权统治。实际上控制了一个人的饭碗,也就可以控制住这个人了。而公权力深入家庭内部,往往会造成家庭共同体成员离心离德,影响文明延续。】
保护这些自由以及其他各项自由的关键是法治。法治与各种不同的自由密切相关,因此斯蒂芬认为,法治本身就是一种自由;因为法治以十分重要的方式为个人提供的各种程序,把个人享有的自由落到了实处。
【注:法治本质上是社会共识的体现,而不仅仅是限制公权力。】
在斯蒂芬看来,法治战胜了专制主义,战胜了某些人为自己的目的而奴役他人的欲望,是一项了不起的道德胜利、一项名垂千古的成就。法治规范并赐予人们各种自由,斯蒂芬虽然认为这些自由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但是他拥护它们,把它们理解为对他极为珍视的文明世界至关重要。
像维多利亚时代他的许多同胞,如阿诺德、梅因、莱基甚至密尔一样,斯蒂芬对他所看到的民主持续扩张的破坏性后果深感忧虑。西元1867年的《改革法案》使英国选民人数翻了一番,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斯蒂芬在撰写《自由·平等·博爱》时推测,扩张地民主政府不会再走回头路,也就是说,建立在普选基础上的政体,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倘若有人问我,你打算用什么取代普选?……我会立刻回答,什么也没有。思想和感情的整个趋势,人类事务的大潮,正势不可挡地朝着那个方向发展。”然而斯蒂芬反驳说,就算实现了普选,普选的辩护者所鼓吹的政治平的的先验信条还是不可能实现:
按你们的意志立法吧,倘若你们认为恰当,就把普选选定为不容违抗的法律吧。但你们离平等仍向过去一样遥远。政治权力的形式变了,其实质却未变。将政治权利切成碎块的后果,无非是让那些能够赢得最大多数碎块的人去统治其他人。这样或那样的强者永远进行统治。若是军事政权,造就伟大军人的品质会使他成为统治者。若是君主政体,国王在大臣、将帅和官员身上所看重的品质将带来权力。而在纯粹的民主政体中,统治者将是那些操纵玩偶的人及其朋党……政体形式的变化更多地改变了上层的状况,而不是它的实质。
【注:《自由·平等·博爱》出版时(西元1873年),英国刚建立基于考试的文官制度(西元1855年设立文官队伍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设立,负责公开招募文官并扫除权贵私荐)。】
尤其令斯蒂芬担忧的是,对民主或政治平等的诉求,常常被错误地当作对自由的诉求。这就把民主、普选——它们跟政治权力的分配有关——与完全属于另一个问题的自由混为一谈了。摆脱日益发展的民主所带来的政治和文化困境的前提是,认识到所谓的政治平等呈现出来的弊端。斯蒂芬在《自由·平等·博爱》一书中所要提供的,正是这种认识。
不管民主有何收益,它也要付出高昂的成本,这使它成了一桩令人沮丧的买卖。“操纵玩偶的人”只要满足无知即可,斯蒂芬担心,这终将导致一种低劣平庸的文化,一种建立在肮脏和庸俗基础上的文化。为了让没教养的人开心,这些新的统治者会把统治延伸到个人生活最隐秘的角落,他们会因此而自愿放弃某些个人自由。
【注:极权主义民主就是这样升起的!】
政治平等的诉求只是平等诉求采取的形式之一,如我们所见,这也正是斯蒂芬认为应当质疑的诉求。更让斯蒂芬担忧的是对纯粹平等的诉求,因为它是个空洞无物的概念。人们需要知道,应当在哪个方面做到平等。然而,把平等作为一种不加限定的价值提出来,它通常是指财产平等。这个意义上的平等尤其与自由相悖:“如果人类的经验证明了什么,它所证明的就是,把限制最小化,把最大程度的自由赋予所有人,结果不会是平等,而是以几何级数扩大的不平等……”勤奋、运气、技能和无数其他因素,必然导致有些人比别人获得和积聚更多的财产,因此行动的自由导致结果的不平等。就算能够消除这种不平等,也只有通过政府不断干预个人追求他们自身目标的各项自由。在斯蒂芬看来,财产平等是自由的丧钟,它为避免这种平等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
【注:财产平等应该就是左衽追求的共同贫穷了,毕竟共同富裕显然是实现不了的。】
斯蒂芬珍视的平等是法律之下的平等,是法治所赋予的平等——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然而法律哲学家们承认,如何确定同等情况,是个大难题。再者,无论这个问题多么棘手,《自由·平等·博爱》的无数当代读者将会发现,至少在生活的一个领域,斯蒂芬对于何者构成同等情况这一问题的理解是有缺陷的。斯蒂芬坚持认为男性优于女性,这不仅表现在体力方面,而且表现在“智力更多”和“性格上更有活力”。男女既然在这些方面并不平等,“涉及两性关系的法律”,例如兵役法和最为专门的婚姻法,就不应对他们同等对待。当然,斯蒂芬着重指出,这种不平等对女性其实是有利的。
【注:我没读过原文,不知道为何加引号。男性平均智商高于女性就像白人智商高于黑人一样早已成为定论,只不过左衽捂着耳朵装听不见罢了。斯蒂芬的看法没错,错的是左衽。不服就让女的也像男的一样跑1000米和做引体向上!】
自由传统留给我们的核心遗产,是世上没有天生的政治权威的观念,霍布斯和洛克这两位自由传统的奠基人对此有极为清楚的阐述。到了西元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这种本来属于政治世界的观念,开始向人类关系更广阔的领域——包括男女之间的各种关系——蔓延。西元17世纪对政治生活中的天赋权威的否定开始向外扩展,导致许多人在19世纪末全面否定等级关系。我们必须把斯蒂芬对男女关系的看法置于这一思想运动的背景之下,因为斯蒂芬要维护一个等级关系既可能又可取的世界。
【注:等级制度本身是人类文明组织度的体现,能有序变化的等级制度是父权制的核心组成成分之一,等级制度需要确保权责对等。】
斯蒂芬把博爱理解为一种天下一家和普世之爱的观念,即社会中的个人首先是因为彼此有相互关爱的感情而结合在一起的观念。斯蒂芬认为,博爱的政治和道德价值的依据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一种脆弱的人性观,它想象有一个世界,那儿不存在个人之间重要的利益冲突及其导致的相互敌对。在博爱的拥护者中间,几乎很少有人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所处的人类社会。因此,博爱的第二个来源是对进步的诉求,只要人类摆脱了各种限制,每个人受到平等等待,人类就能取得进步;正是因为进步而焕发出新活力得人性,使博爱成为可能。
【注:斯蒂芬作为基督徒,不信兼爱思想,恐怕是因为不能兼爱到异教徒或异端头上吧!此外,天下不等于世界,天下本质上是以儒家中国为宗主的封建体制的范围,普世宗教或普世价值的应用范围是世界。】
可是,在斯蒂芬看来,更冷静的思考揭示了人性和博爱是不相容的。他说:“
我则相信,有不少人是坏人,但绝大多数人既不好也不坏……这个无所用心的广大群体随着环境左右摇摆……我还相信,在所有类型的人之间,都存在并将永远存在敌意和冲突的真正诱因,甚至好人也有可能相互为敌,他们经常是被迫如此,这要么是因为存在着使他们发生冲突的利益之争,要么是因为他们对于”善“有着不同的理解方式。
博爱的辩护者对消除人类生活中的大量仇恨和罪恶信心满怀;但在斯蒂芬看来,人类状况中的这些基本因素,尽管能够通过道德、宗教和法律得到一定的改善,确实源于人性的永恒特征。斯蒂芬宣称,导致个人不和的不同利益,还有不同的”善“观念,都是无法消除的人性特征。他进一步认为,人类的状况所固有的各种利益和价值冲突,不仅导致个人之间的对抗,而且导致群体之间的对抗。例如,他推测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会一直相互敌视,因为他们有着迥然不同的善恶观。
【注:这个推测显然有问题,现在显然流行基督徒皈依伊斯兰教了。如德国东德勃兰登堡州(Brandenburg)右翼党派领导人瓦格纳(Arthur Wagner)作为德国反穆斯林党派的高级成员,竟然自己皈依了伊斯兰教,这很讽刺。】
斯蒂芬认为,那些急不可耐地渴望博爱的人,不但无法在人世间为博爱找到一块安身之地,而且很容易给现实生活造成恶果。
一个人的思想和感情,他对现状的评估以及他针对现状采取的行动,只要真沾上了这种【博爱的】理想,那么正如经验一再表明的那样,他通常会为了他本人所理解的后代的幸福,毫无犹豫地牺牲现在活着地人所理解的幸福。
普世之爱经常患上狂热症。博爱的诉求表面上打着世界一家的招牌,骨子里却很少关心现实中的人。博爱的鼓吹者认为,我们实际看到的人不符合标准,所以为了那些仅仅存在于抽象的理论世界的人,可以轻易把这些人抛进现实世界的垃圾箱:如果以博爱为动力的世界前景危在旦夕,现在这些人的自由和幸福又算得了什么?
如前所说,斯蒂芬在《自由·平等·博爱》中所阐述的他本人的立场,是贯穿于全书他对密尔的批评之中的。斯蒂芬十分敬佩早期的密尔,即写作《时代精神》、《论文明》、《边沁》、《逻辑体系》第四卷(《论道德哲学的逻辑》)和两篇《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的密尔。其实,西元1859年《论自由》面世时,斯蒂芬很赞赏此书。然而,1867年的《改革法案》,在印度的经历,密尔《论妇女的屈从地位》的出版,以及他本人的深入思考,使斯蒂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后来的密尔已经抛弃了斯蒂芬所理解的英国自由主义原则。
正如斯蒂芬所说,《论自由》犯下了一大堆错误。密尔的”简单自由原则“认为,只有防止损害他人的限制才是正当的。人类的状况太复杂,这条原则是不适用的;为密尔的自由原则提供基础的区分,即利己行为和利他行为的区分,无法用清晰的方式阐明;密尔的自由原则与他的功利主义方枘圆凿,密尔的自由原则要求人类事务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这种状况将导致懒散和恶习,而不是密尔(仿照威廉·冯·洪堡)所想象的自我发展;缺少得到民意支持的道德约束,自由将变成放纵,没有任何社会价值;思想自由并不像密尔设想的那样趋向于真理;一丝不苟地采用密尔的自由原则,它将颠覆一切道德,因为道德是通过他人的强制性意见体现出来的。
斯蒂芬对密尔《论妇女的屈从地位》和《功利主义》的批评比较简短,严厉程度却不减:前一本著作使我们对男女之间恰当的关系产生误解,并且助长一种侵害高级文明和自由的民主观;后一本著作暗示世界一家是可能的,这与事实严重不符,也是对自由的破坏。
【注:就算地球都是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或马教的地盘,那么在扩张到极致之前,它们本身就会分裂互砍,从这角度看,兼爱也只能是一种幻想。】
可以公正地说,斯蒂芬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解,几乎在所有重要的细节上都与密尔相反。在他看来,他支持自由,密尔则主张放纵;他支持法律之下的平等,密尔则支持一种乖张的平等主义;他主张清醒地理解人类生活中地冲突,密尔则赞成一种巨大的幻想。
不必否认,斯蒂芬至少在有些时候误解了密尔的学说,没有留意某些可以从中看到的精髓,他对密尔的一些指责也有失偏颇。不过同样真实的是,斯蒂芬从密尔的思想中看到了一些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他的许多评论切中要害。更为重要的是,斯蒂芬本人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诲的性质——一直受到不恰当的忽视——无疑值得我们关注。
在英美哲学界霸气十足的分析传统,会让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斯蒂芬的政治哲学,最好是把它理解为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事实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有过很多思想努力。不消说,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什么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进行冗长细致的分析,这无论如何都是一项困难重重的任务,而且让人拿不准的是,根据抽象、永恒和非历史的范畴去理解斯蒂芬的政治哲学,是否有任何益处或重要性。
然而重要的是,斯蒂芬的确把自己理解为古老的英国自由主义的卫士。在斯蒂芬看来,我们不应该把这种自由主义理解为抽象的哲学范畴,而应当理解为一种政治生活形态的概念,历史地看,这种政治生活形态在西元19世纪中叶的英国深入人心。它珍视有秩序的自由,惧怕放纵,既厌恶专制政治,又惶恐不安地看待普选制。斯蒂芬所信奉的英国自由主义,看重”在政治事务上豁达高尚的情感,它的引导者有着高度教养、开阔的胸襟和不偏不倚的理智“,而不是卑琐粗俗的习气,斯蒂芬相信这种习气会出现在另一种政治生活的观念之中,他认为密尔的著作便诠释和预示着这种观念。
就像西元19世纪后期的维多利亚英国一样,我们的世界也在思考自由、平等和博爱。环顾四周,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哲学领域——这个著名的三位一体的精彩画像。然而许多画像如同雾中花、镜中月,我们往往很难弄清楚我们从中看到的是自由还是放纵。这想必是一个重大问题,斯蒂芬的《自由・平等・博爱》堪称一本杰作,它能帮助我们清晰地理解拿给我们看的是什么货色。更大的意义在于,在一个继续娇惯各种博爱和平等的世界里,斯蒂芬对它们的驳斥或可提醒我们:博爱与平等牺牲的是自由,而不是放纵。 这也许能引导我们更加认真地思考我们所能得到的回报的性质。
編者説明
第一版 前言
第一章 自由概説
本书旨在考察一些教义,它们与其说是”自由、平等、博爱“这句口号所明示的,不如说是它暗示的。这句口号已经成为不止一个国家的座右铭。事实上它不仅是一句座右铭,还是一种宗教的信条,但是这种宗教并不像基督教的任何一种形式那样明确。基督教既是它的竞争者,又是它的敌人,还是它的同伙,但它的力量并不因此而稍减。恰恰相反,它是当今最深入人心的一股势力。它不时展现自己清晰的身段,实证主义便是它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最著名的形态之一,但它的特定面貌却无法让人一窥堂奥。它渗透进另一些信条,时常把基督教改造成一种乐观主义体系,对基督教的用语既有所取用,也有所舍弃。它深刻地影响着政治和法律。它有自己的神圣节日,有自己冷静的信徒,也有狂热的追随者,它有自己的再洗礼派和唯信仰派。”人性教“这个字眼,相对于孔德赋予它的狭隘的专业含义,如果能够再更宽泛的含义上使用,或许是我们能为它找到的一个不错的名称。它是当今最普遍的信念之一,它把各种光辉灿烂的前景呈现于人类集体面前,只要废除对人类行为的一些限制,承认全人类实质性的平等,奉行博爱或普世之爱,就能发现通向这些前景的道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教义被人尊奉为宗教信仰。它们不仅被看作真理,而且被信徒们看作要随时为之而战的真理,为了使其得到确立,他们准备牺牲一切个人目标。
这样说当然是很笼统的,但它就是我将”自由、平等、博爱“视为其信条的那种宗教。我是不信这种东西的。
【注:斯蒂芬居然能认识到卢梭宗是基督教的衍生品,这眼光还是不错的!值得称赞下!】
……
言归正传。本人认为,以下内容是对《论自由》的导论,即该书最重要的部分,所做的公正概述。
该书的主题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它有别于”所谓的意志自由“(《论自由》,5/217)。密尔告诉我们,这个概念最初是指保护人们免于政治统治者的暴政。统治者的权力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恶,通过权利或宪政制衡去限制这种权力,便是自由的含义。后来,人们开始把他们的统治者视为自己的代理人和自己权力的受托人,而不是需要制约的对立的权力,在他们看来,他们通过代理人行使自己的权力,不会像他们的统治者在或严或宽的限制下的权力那样具有压迫性。然而经验逐渐表明,全体有可能对部分实行暴政,它决非没有这种倾向, 于是便有了”多数的暴政“(《论自由》,8/221)一说。多数的暴政源于”人人心中都有一种感情,要求每个人应当以他及与他有同感的人所喜欢的方式去行动。“(《论自由》,9/221)密尔先生对此做了一番说明之后,接着说:”在思想和感情方面走在社会前列的人,并没有从原则上谴责这种状况,尽管他们在其中的某些细节上会与它发生冲突。他们致力于探讨社会的好恶应当针对哪些事情,而不去探究社会的好恶是否应该成为针对个人的法律“。(《论自由》,11/222)然后他用下面这段话阐明了观点:
本文的目的是要力主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使凡属社会以强制和控制方法对付个人之事,不论所用手段是法律惩罚方式下的物质力量或者是公众意见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准绳。这条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各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若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处,那不成为充足的理由,人们不能强迫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或者不去做一件事。说因为这对他比较好,因为这会使他比较愉快,因为这在别人的意见认为是聪明的或者甚至是正当的;这样不能算是正当。所有这些理由,若是为了向他规劝,或是为了和他辨理,或是为了对他说服,以至是为了向他恳求,那都是好的;但只是不能借以对他实行强迫,或者说,如果他相反而行的话便要使他遭受什么灾祸。要使强迫成为正当,必须是所要对他加以吓阻的那宗行为将会对他人产生祸害。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个人对于他自己、他自己的身体和思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论自由》,13/223-224)
他指出:”这一条原则只适用于各项能力已经成熟的人类,“(《论自由》,13/224)“至于那些其种族可以被视为处在未成年期的落后的社会状态,我们可以不予考虑。”(《论自由》,13/224)他接着又说,能够“从完全与功利无关的抽象权利观”得出的任何有利于他的论证的东西,他一概弃之不用。他补充说:“我把功利视为一切道德问题的最终裁决者;但这里所说的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它的基础是不断进步的人的长远利益。”(《论自由》,14/224)他最后具体说明了——
但是也有这样一类行动对于社会说来,就其有别于个人之处来看,只有(假如还有的话)一种间接的利害。这类行动的范围包括一个人生活和行为中仅只影响到本人自己的全部,或者若说也影响到他人的话,那也是得有他们自由自愿的、非经蒙骗的同意和参加的。必须说明,我在这里说仅只影响到本人,意思是说这影响是直接的,是最初的:否则,既是凡属影响到本人的都会通过本人而影响到他人,也未可知,那么,凡可根据这个未可知之事而来的反对也势须予以考虑了。这样说来,这就是人类自由的适当领域。这个领域包括着,第一,意识的内向境地,要求着最广义的良心的自由;要求着思想和感想的自由;要求着在不论是实践的或思考的、是科学的、道德的或神学的等等一切题目上的意见和情操的绝对自由。说到发表和刊发意见的自由,因为它属于个人涉及他人那部分行为,看来象是归在另一原则之下;但是由于它和思想自由本身几乎同样重要,所依据的理由又大部分相同,所以在实践上是和思想自由分不开的。第二,这个原则还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要求有自由订定自己的生活计划以顺应自己的性格;要求有自由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当然也不规避会随来的后果。这种自由,只要我们所做所为并无害于我们的同胞,就不应遭到他们的妨碍,即使他们认为我们的行为是愚蠢、背谬、或错误的。第三,随着各个人的这种自由而来的,在同样的限度之内,还有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这就是说,人们有自由为着任何无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联合,只要参加联合的人们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骗。
我认为,这就是导论一章的基本教义。它也是该书的全部教义,值得注意的是,密尔先生全面细致地阐述了他的教义,却从未试图从整体上去证明它。他也许想在第二、三、四章分别证明这种教义的不同内容。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把第二章当作为证明思想和言论的绝对自由是有益的而提出的论证。同样,第三章是为证明个性乃幸福的要素提供的论证,但它仅仅假定而非证明了自由是个性的前提,这是大可商榷的。第四章的标题是“论社会对个人行使权力的界限”。它仅仅具体重申了导论一章提出的一般原则。它没有为整个论证增添任何内容,只有下面这段话除外,它无疑需要给予重视:“反对公众干涉纯粹私人行为的最有力的论证是,当它进行干涉时,多数情况下它是在错误的场合进行错误的干涉。”(《论自由》,83/283)最后的第五章题为“原则的应用”,如题所示,这一章是讲把一般原则运用于某些具体事例。
通观全书,几乎没有任何与他对上述原则的阐述和声明有所不同的内容可以被恰当地称为证明。然而我认为,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这条原则非常需要证明。为了证明这一点,首先有必要根据我认为密尔先生和我本人一致赞成的原则,指出“自由”一次的含义。我想,对以下人类行为理论的表述,密尔先生是不会提出异议的:一切有意识地行为都是因动机而发生。一切动机都可以分为两类:愿望和恐惧,快乐和痛苦。以愿望为动机的有意识的行为可以称为自由的;以恐惧为动机的有意识的可以称为被迫的,或者说是受到限制的。以女人出嫁为例,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意识的行为。如果她以正常的感情看待婚姻,出于正常的动机出嫁,那就可以说她的行为是自由的。如果她认为结婚是出于迫不得已,她出嫁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灾祸,那就可以说她的行为是被迫的,是不自由的。
如果这是正确的自由理论——尽管许多人会予以否认,我想密尔先生会接受它——那么前述主张就可以概括为:“无论是谁,除非是为了自卫,试图通过引起别人的恐惧去影响其行为是不正当的。”或者,换一个估计密尔先生也会赞成的说法:“除特殊情况之外,利用人们的恐惧去影响他们的行为,绝对不能促进人类的普遍幸福。”
这些说法想必不能被看作是自明的,它们甚至与谬论相去不远。全部道德和全部现有的宗教都在致力于影响人类的行为,它们只诉诸希望或恐惧,并且诉诸恐惧比诉诸希望普遍得多、明显得多;既然如此,该如何看待它们呢?刑法本身可以被看作禁止的手段,它与耶和华批准的道德观和道德形式相比并不更加重要。一个人的某种行为因惧怕当地的法律而受到限制,却有许多人的不计其数的行为因惧于四邻的非议而受到限制,这就是道德的惩罚;或因担心来世受罚而受到限制,这就是信仰的惩罚;或害怕内心的不安而受到限制,这也许可以成为良心的惩罚,或是把它视为前面两种惩罚的混合。在数不胜数的很多情形下,众人的非议,或道德的惩罚,都与自卫不相干。信仰的惩罚从本质上说也与自卫无关。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它的基本前提是以最大程度的不宽容去对待罪恶,惩罚它绝不手软,不管它存在于何处,除非有某些特殊的规定。我并不是说这种教义是正确的,但是我的确认为,不经任何证明,谁都没有资格假设它在本质上是不道德的、有害的。密尔先生没有做这种推论,我却认为他的理论包含着这种推论,因为我知道,与他的自由学说最不相符、最南辕北辙的,是这样一种教义:有一个法庭或判官,在这个法庭上,或在这个判官面前, 人人对自己的肉体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如实交代,无论它是否出于私心。按密尔先生的学说,审判日那天,一个人说“我只是给自己找乐,并未侵害他人”,这应该的一句很好的辩词。是否真有这样的审判日,不是问题之所在,但是按他的原则,“审判日”这种观念根本就是不道德的。按他的原则,对任何人进行惩罚而又不是为了保护其他人的耶和华,不啻是一个践踏自由的暴君。
【注:按《新旧约全书》,耶和华确实是个践踏自由的暴君!】
把这条原则应用于道德惩罚,将无异于颠覆人们普遍认可的全部道德。唯一能与密尔先生陈述的原则相适应的道德原则,可以概括如下:“自寻其乐无妨,伤害他人莫为。”任何道德原则,如果它的目标不限于此,而是除了免于伤害之外还要为全社会带来福利,或是为受其影响的人做些好事,从原则上讲都是错误的。这等于谴责所有现存的道德体系。实际上,积极的道德无非是一套原则和规矩,它们的表述或多或少是含糊的,它们或多或少是含糊的,它们或多或少有待于人们自己去理解,因为有它们,一些行为方式在道义的普遍谴责之下受到禁止,这与自我防卫毫不相干。
【注:挤掉吸血的国企职工或是枪毙连环杀人犯,算是伤害他人吗?集体利益的边界在哪?单纯追求帕累托最优下的效用最大化,终归还是有问题的。】
密尔先生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这一点。他在《论自由》第四章的开头部分说,一个人如果严重欠缺增进自己利益的品质,那么他“必然成为也应该成为人们厌恶的对象,或在极端的情形中,甚至成为人们鄙视的对象”(《论自由》,77/278)。接着他列举了这种欠缺会给人带来的种种不便。不过,他又补充说:“一个人的行为和性格中,只涉及自己的利益而对他有关的人们的利益没有影响的那一部分,倘若遭到他人的非议,他所应承担的只是与这种非议密切相关的那些不便。”(《论自由》,78/278-279)这无疑使他对积极道德的承认打了折扣;但不管怎么说,事实依然是:道德是而且必须是一种禁止性的体系,它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大家树立一个行为和情感标准,如果它不是为了对他们施加限制,很少会有人遵守这种标准。几乎在所有情形下, 这种道德体系的作用,都大大超出可以被称为自卫的事情的范围。
【注:上面这段貌似在说强制才能使道德成为禁止性体系。】
密尔先生的学说不仅有悖于所有与道德有关的神学体系、有悖于所有众所周知的积极的道德体系,而且有悖于人性本身的构造。人类普遍视为良好的每一种习惯,几乎都需要经过或多或少痛苦而艰辛的努力才能养成。由人类生活的状态所决定,我们生活中的几乎每一种行为,必然受到环境的限制和强迫。那么,自由为什么还会像密尔先生所定义的那般珍贵呢?对于在我们生活中任何时候都没有受到环境限制的行为,立法者或其他人却因为不赞成它——或者换一个说法,因为讨厌它——而动员舆论加以控制,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呢?惩罚杀人和偷窃的法律取代了个人的复仇,如果没有法律,这种复仇尽管采用不正规的方式,会对罪行施以更严酷的惩罚。如果有惩罚放荡、贪食和酗酒的法律,那么对它们也可以这样说。
密尔先生在很多地方承认:“有些不便是与他人的非议分不开的。”(《论自由》,78/278)那么,这些不便,与另一些类似的不便——它们是有组织、有规定的,是按证据施加的,但环境也要求施加这种不便——之间有什么原则上的区别吗?这种组织、规定和程序使密尔先生所赞成的限制与他所反对的限制判然有别。但我看不出这种区分的依据何在。我也无法理解,为何用罚款、监禁或剥夺公民权去惩罚酗酒行为必定总是错误的,而通过“与他人的非议密切相关的”结果去惩罚这种行为,必定总是正确的。也许可以说,这些结果的发生,不是因为我们想让它那样,而是因为它符合自然的普遍秩序。然而这种回答只会带来进一步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自然应当被看作朋友还是敌人?每一个明事理的人都会回答说,对他们的非议的畏惧给我们的行为施加的限制,是天性的一部分,而天性是最不受我们摆布的。但是,倘若真是这样,为什么要像密尔先生那样划出那条界限呢?为什么还要将他人的非议的惩罚性后果最小化,把它限制在最狭小的范围呢?“与他人的非议密切相关的”“不便”究竟意何所指?如果整个社会完全采用密尔先生的自由学说,大大减少这些不便并非难事。邻居的个人性格与我们何干——大力鼓吹并严格实行这种教条,那么所形成的非议的数量,以及它所造成的不便的数量,可以减少到如我们所愿的程度,自由的范围也会得到相应比例的扩大。明事理的人真希望这样吗?有谁愿意看到公然的放肆、极度的放纵、荒谬的自负或诸如此类的现象被漠然置之,或在知情的情况下让它们造成本来可以避免的不便呢?
如果对不道德行为的限制是保护社会免于毁灭性影响的主要手段,为何要将它看成坏事呢?何必在社会惩罚和法律惩罚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呢?密尔先生以各种说法断定这种区分是存在的。他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十分清楚。可是我把《论自由》从头翻到尾,也没找到这种区分的任何证明,甚至没有看到他打算提供一个合理而恰当的证明。如果他的学说是正确的,它就应当可以得到证明。没有证明,是因为它不正确。
我认为,为了使这些主张的每一条都能够成立,可以援引那些与自卫无关的强制中最常见、最重要的事例。其中最重要的事例包括:
一、旨在确立和维护宗教信仰的强制。
二、旨在确立和在实践中维护道德的强制。
三、旨在改变现行政治或社会制度形态的强制。
从语言的惯用含义上说,这些强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被描述为自卫或防止对施以强制者以外的人造成伤害的事例。它们都属于强制的事例,目的在于达到行使强制性权力的人认为美好的目标,因此密尔先生的原则对它们一概予以谴责,其中的第二和第三项强制,是他的原则确定无疑打算予以谴责的对象。如他所说,他的原则其实比这走得更远。例如,它可以谴责未经纳税人同意的一切征税,除非征来的钱是用于军事、治安或司法目的,因为只有这些目的可以被描述为自卫。强迫不情愿的人为大英博物馆捐款,无异于宗教迫害,显然这违反了密尔先生的原则。但他没有注意或坚持这一点,对此我只想说,这证明了与他认为必须说明的限制限制相比,他的原则需要更多的限制。
还是回到上述三种强制上来吧,我认为,密尔先生不仅有义务证明这些强制有坏作用——如果我们说外科手术也有坏作用,岂不是废话?——他还得证明这些作用来自强制本身,与强制的目的无关,也与采取强制者的错误和过激行为无关。他不能只说手术很痛苦,或截肢很不幸,医生往往粗鲁或技术不精,他还得证明作为一门技艺的手术在本质上就是有害的,应该予以禁止。我要说,他在这本书里,从头到尾都没想证明这一点。即使他想证明,他也会发现,这是一项徒劳无功的任务。
关于旨在确立和维护宗教信仰及道德体系的强制,坚持以下原则无异于浪费时间:宗教和道德在整体上是有益的,尽管存在着与之相关的种种不幸。我无须重复前面就此说过的话,宗教和道德限制在本质上是而且必然总是强制系统。然而,一旦把这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就有必要更充分地思考道德和宗教限制的本质,以及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如果始终采用密尔先生的自由观,并让它全面发挥作用——如果它是最早的基督信徒或穆罕默德信徒的观点——我们就会发现,世上根本不会出现有组织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即使在它们和另一些宗教获得成功之后,广大人类群体的道德也只是发挥着他们乐意让它发挥的一些作用,其范围局限在害怕非议而形成的习俗对人们施加的限制之内。以厌恶的态度看待某些行为的习俗,乃是道德的本质。人的行为引起厌恶,这个人感受到这种厌恶,或者把它说成是因为他本人良心的作用引起,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不必在这里讨论。重要的是,除非那些有不同寻常的能力去感受非议的人——并且他们的地位使他们能够让别人接受他们的原则甚至他们的喜好和感情——把这种非议施加于人类,不然这种非议是绝对不会成为习俗的。
总之,正如我们所知,宗教和道德其实都被打上了遵照命令而建立的印记,即使在它们最祥和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对宗教的建立已有足够的了解,十分清楚它们通常走过的道路。宗教先是由一个人或一小撮人宣扬。有些信徒热诚接受了它,通过宣扬、说服和感化的力量,把他们的观点传给世人,直到新的信条有了足够的势力,建立了足够好的组织,可以对自己的成员和他人行使权力。如果宗教信条活力四射,这种权力会表现为多种形式。如果最早的皈依者是战士,它可以是军事力量;它也可以是一种来世的威胁力量——这是我们有实际体验的最普遍、最明确的宗教权力形式。它可以来自纯粹的、卓越的意志,或是来自拥有这种意志的人用它来创造的组织。但是,不管宗教力量的具体形式为何,有一条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即宗教的成长从本质上说是一小群热诚的信徒征服人类中那些冷漠麻木的人以及自愿的无知者的过程。……人们的生活就是通过这些工程——也就是说,通过各种各样的习俗和制度——进行管理的。这些习俗不仅从本质上说是各种限制,而且它们是由极少数人的意志施加的限制,多数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些限制,在他们看来,这些限制已变得如此自然,以至于并不把它们当作限制。
【注:这段表明斯蒂芬对宗教起源的认知是正确的。这很值得我们学习,比如我们可以学习摩西的手段来为儒教打上最需要的补丁。“铁甲依然在”!!!】
至于第三种情况,即十分常见的限制——我是说旨在改变现有政治和社会制度形态地强制——无须论证即可表明,过去三百年里作为欧洲历史主旋律地所有政治大变革,都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强制的事例。虽然其中的很多变革被说成是一些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其实他们却最强有力地行使着权力。
……
宣称所有这些事例中的暴力都是不正当的,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密尔先生大概是最不愿意坚持这种自相矛盾的人。宣称暴力只有在为自卫所必需时才是正当的,是无法对事实做出解释的。看看创立新宗教、让旧信仰退化为无伤大雅的私人观点的事例吧:人类的生活在假定古老信仰为真的基础上,世世代代地延续着,一个国家的广大民众并没有打乱现状的特别愿望,尽管他们可能已经不再相信它所包含的信条;出现了抨击腐败、鼓吹新教义的改革者,他们受到惩罚,他们进行抵抗,于是形成了宗派,由此产生了充斥于历史之中的各种结果。从什么意义上能够说,这类事情中发生的暴力行为是自卫行为、是防止伤害他人的行为呢?这些行为是侵犯既有体制,后者被认为是恶劣的体制,并且人们看到了可以用来取代它的被假定为更好的体制。如果有人认为,在涉及这种转变时,可以在当做与不当做之事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如果有人信心十足地说,法国大革命或宗教改革应该如何如何进行,这样既可使双方避免一切暴力,又可获得可取的结果,这人便能够为我们提供一部通用的政治宪法和一部通用的法典了。像查理五世、菲利普二世、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路易十六这类人,处在他们的位置上,必须选择一派,必须尽全力支持它,反对它的对手,除非他们想自取灭亡。
【注:确实,选边站才是常态,让所有人都满意只是妄想。】
能够使这种情况与密尔先生的原则相互调和的唯一方式,是把这种暴力称为自卫。如果这样来解释“自卫”一词,使它包括一切为改变现状而采取的暴力行动,那就只能说,倘若人们恰好生活在一种政治或社会制度之下,如果他们不满于它的原则或运行状况,可以为了分歧而大打出手,获胜者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解决争议,这将使密尔先生的原则变成荒唐的谬论。另一方面,如果不把为改善现状而采取的暴力行动说成自卫,那么任何这样的行动都是不正当的,除非为了直接保护当事人而必须这样做。这还是一个谬论。
其实,自卫和至于个人有关的行为的原则,并不是一个可以用来判断革命是对是错的标准,因为他所依据的是一种大错特错的区分。它假设有些行为只涉及当事人,有些行为涉及其他人。其实,我们的行为中最重要的部分,同时涉及我们自身和其它人,革命就是这一点的确凿证据。所以说,密尔先生的原则并不适用于最需要这种原则的事例。它假设存在着一种理想状态,人人都关心所有人的福祉,而且都恰好处在他应处的位置上。倘有这种状态存在,则我们说为了维持现状,任何人都不可干涉其他人,除非为了使自己免受攻击,便还有些道理。可是现在并不存在这种状态,任何年代或国家也从未存在过这种状态,所以密尔先生的原则是不能成立的。
【注:下面斯蒂芬批驳密尔的“他的原则只适用于各项能力已经成熟的人类。……至于那些种族可以被视为处于未成年期的落后社会状态,我们可以不予考虑”。斯蒂芬认为对成年人的行为管理也同时需要强制和说服。】
看看反映在法律和制度中的人类团体的行为,我们会发现,从最不成熟、最野蛮的年代和社会,到最文明的年代和社会,尽管强制和说服并存,我们获得大多数最好的成功都要归功于强制,讨论充其量只起着动员作用,它或许能促使强者运用他们的力量。
“本书中所要讨论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民族”,已经进入了人类“能够通过自由平等的讨论获得改善”(《论自由》,14/224)的时代——评估这一主张的正确性,可以参照人们熟知的两种观点:
一、人类对于把人本身作为主要对象的主题,如宗教、道德和政治,大体上处于无知状态,较为有利的情况,也仅仅是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就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具备的知识而言,自由的讨论能够走多远呢?我们充其量能够指望——人们也只有这点儿能耐——某些常识多少会得到普及,以其现状看,它们顶多是些残缺不全的真理。……
【注:下面举例说明这个论点,比如理解亚当·斯密的人远没有笃信穆罕默德的人多。。。】
二、由人类的天性所定,不管我们采用哪一种善恶学说,世上总是存在着大量的坏人和无所用心的人,他们故意做他们不应该做的事,却把他们当做之事置于脑后。男男女女中有自私自利、感情用事、轻率、懒惰的人,有人云亦云、陷于琐碎的日常事务不能自拔的人,先想想这些人占了多大比例,再去考虑最自由的讨论能把他们提高多少吧!对他们有实际作用的唯一办法,就是强迫和限制。我在此不想深究是同时还是分别采用它们更有价值,本人只想说,哪怕给他们天大的自由,也不能让他们有分毫的改进。
【注:确实是这个道理。”古之学者为己“,为己不易啊!】
第二章 論思想和辯論的自由
我在前一章指出,密尔先生只是宣布了他的自由学说,却没有给予证明。不过,《论自由》第二章”论思想和辩论的自由“及第三章”论个性是福祉的要素之一“,或可看作对他在导论中提出的一般原理的部分内容的论证或它们的应用,所以我要谈谈这两章的内容。我所反对的,不是密尔先生的实际结论,而是他的理论。下面我希望表明我们在实践上的分歧扩大到什么程度。对于他关于自由问题的大多数论述,我的意见是,他为了在实践中证明一些只能用狭隘的特殊理由才能证明的事情,建立了一种本身并不正确的理论,倾向于肯定那些在实践中有害的观点。
”论思想和辩论的自由“这一章的结论,密尔先生以他特有的言简意赅的风格,做了如下概括:
至此,我们已经从很清楚的四点根据上认识到,意见自由以及意见表达自由对人类精神幸福(它决定着人类的其他一切幸福)的必要性了;现在我们就来扼要地概括一下。
一、即便某一意见被压制而至于沉默,但其实我们未必真的不知道,那个意见有可能是正确的。拒绝承认此点就是认定我们自己绝对不会出错。
二、即使被压制的意见是错误的,它也可能包含并且通常确实包含部分真理;而由于在任何主题上,普遍或通行的意见难得是或从来不曾是全部真理,只有通过与反面意见的碰撞,余下的部分真理才有机会得以补足。
三、纵然公认意见不仅正确而且是全部真理,除非它允许并确实经受了极其有力而又最为认真的挑战,否则大多数接受它的人抱持的仅仅是一项成见,对其所以然的理性根据毫无理解或体认。
四、不宁唯是,信条本身的意义也将变得岌岌可危,其可能由隐晦而至于消失,对人的身心言行将不复有积极影响的能力:最终,由于信仰仅仅剩下形式,非但无益于为人增福,而且还因破坏了根基,从而妨碍了任何真实而又诚挚的信念自人类理性或个人体验中生长出来。
……
但是这一章留给我的印象是,为了确立这一有限的实践性结论,密尔先生提出了一种理论,它其实离真理十分遥远,一旦这种理论被普遍接受,有可能对合理的立法造成严重障碍。
作者赞成在所有问题上发表意见的无线自由,他的第一条理由是:”假如某种意见被迫保持缄默,我们便无法确知它可能是正确的。否定这一点等于假定我们具有无谬性。“
……
这一回答并不能令我满意。对作为其基础的论证加以分析,使之具有清晰的形式,并不是十分容易。但是我想,这要以对下面几个命题的考察作为基础:
一、谁都不可能对任何意见的正确性提供合理的保证,除非他是无谬之人,或者,除非人人都有绝对的自由的反驳它。
二、凡是阻止任何意见之表达的人,也就是在通过这种行动断言,他能合理地担保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三、他同时也破坏了使他作出的断言为真的合理担保得以成立的一个条件,即其他人反驳他的自由。
四、因此,他是在主张自己具有无谬性,这是能够保证其断言为真的唯一依据。
第一条和第二条在我看来是错误的。
……
简而言之,在我看来,密尔先生的论点不适用的情形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可以根据证据获得道德确定性的情形,二是无法根据证据获得这种确定性的情形。
如果根据证据能够获得道德确定性,那么对意见的压制并不包含无谬性主张,而是顶多包含在特定情况下正确的主张。
如果依据证据无法获得道德确定性,对意见的压制也不包含无谬性主张,因为它没有断定受到压制的意见是错误的。
赞同思想和言论无限自由的其他三条论证分别是:一、受到压制的意见或许是部分正确的,只有通过讨论,才能使这一部分真理显现出来。二、正确的意见除非经过激烈而真诚的辩论,不然便无法让人相信它是正确的。三、除非经过讨论,否则它会被人们以墨守成规的方式持有。
这些论证所表明的,不是对意见的压制从来不可能正确,而是有时候它可能错误,没有否认这一点。这些论证中没有一条证明了——如果第一条论证是有依据的,它本来是可以证明的——在任何情况下对一种学说的迫害行为都包含着明确的知识错误。就第一条论据而言,如果有人随时打算把有可能完全正确的主张当作有可能完全错误的主张加以迫害,那么他们显然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仅仅部分正确的主张。第二和第三条论证——下面我还要谈到它们——只适用于特定的一小部分人,这些人的意见主要依靠他们通过正确的认知过程而获得的个人意识。无以计数的大多数人,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形成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能吸引他们,是因为投他们的脾气,符合他们的愿望,而不是因为他们一向有证据的担保,能够相信自己是正确的。思想和辩论的无限自由的恶果是,它使很多很多头脑对众多问题产生普遍怀疑。如果你需要狂热的信仰,那就让人们大打出手。人们因为意见进行迫害,或因为意见受到迫害,大概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让人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意见多么重要、别人的意见何等邪恶了。言论的无限自由也许是件大好事,但它并不倾向于对所持意见的意义产生热情,甚至不倾向于对它作出明确的评估。它只会使双方对和那些意见有关的事情产生强烈兴趣,而这种兴趣是非常个人化的,根深蒂固的,外在的限制几乎不能对产生影响,当然,如果它是这种限制所激起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注:以前我能想到的反驳言论无限自由的事例都是和一神教有关的,特别是害死无数人不偿命的马教理论。这里斯蒂芬对这种思想的反驳还是挺有参考价值,虽然我没怎么看懂(毕竟我有先入为主的杂乱无章的一些想法)。下面斯蒂芬主要强调纪律、管教、限制的重要性,反驳和个性有关的”解除限制通常倾向于使人格充满活力“这一假定。】
我对这个问题所要说的大部分内容,之前在《弗雷泽杂志》的一篇文章都已说过。它对以下几点主张予以大力阐发和说明,在我看来它们是无可辩驳的:
一、民主意义上的自由的增长,倾向于减少而不是增加独创性和个性。”只要法律能使人人平等,那就使他们平等好了,但除了使每个人在压倒性的多数面前变得彻底软弱无力之外,这种平等还能意味着什么呢?“这种社会状态的存在使个人变得软弱无力,这时给他们说什么要强大,要有原创性和独立性,无异于嘲笑他们。这就像为了让飞禽变成走兽而拔掉它的羽毛,却仍要让它飞翔一样。
二、”简单地消除各种限制,人们就会变得更有活力,这就像指望种在开阔地上的一棵灌木会自然长成森林里的大树一样虚妄。需要加强的是内在的力量,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力量甚至会越发产生更大的作用,以便不使自身耗散。“
三、尽管有多种多样的善,但多样性本身并不是善。”如果有一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很清醒,相对于另一个一半人清醒一半人酗酒的国家,尽管它的多样性较少,但它会更幸福、更美好、更进步。
【注:上面三段言论都是针对个性说的。第三条问题多多,这里暂不反驳。】
对密尔先生有关的这个问题的观点就说这么多。下面我要阐述我本人对一般意义上的自由,特别是思想自由的观点。
自由是好事还是坏事的问题,就像火这个东西好不好一样,在我看来都不是合理的问题。它既是好事,也是坏事,这要依地点、时间和环境而定。至于什么情况下自由是好事,什么情况下不是好事,全面回答这个问题,不但涉及人类的全部历史,而且涉及对这一历史所提出问题的全面解答。我不相信我们的知识状况已经使我们能够阐明“一条非常简单的原则,在社会以强制或控制的方式对待个人方面,它具有绝对的主宰权”(《论自由》,13/223)。我们必须以更加谨慎的方式,只限于评论经验显示给我们的事情,即在特定情况下自由和强制各自具有哪些利弊。
以下陈述不是、也不敢冒充是对“在什么情况下自由是件好事”这个问题的解答。我只想表明,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应该如何进行讨论。它符合我跟密尔先生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接受的伦理学一般原理,所以我看不出他会否认它的正确性。
强制在以下情况中是有害的:
一、强制的目的是有害的。
二、强制的目的是正确的,但使用强制手段不适合达到目的。
三、强制的目的是正确的,使用强制手段也适合达到目的,但付出的代价过高。
因此,强迫一个人杀人是有害的,因为目的是有害的。
对坚持特定的宗教观点进行惩罚——足以激起愤怒,却不足以阻止或消灭这种观点——是有害的,因为即使强制的目的正确,它也不适合达到目的。
设下触发枪打人,以此迫害人们不侵入私人林地是有害的,因为它造成的危害处远远大于它试图避免的危害。
然而,如果目的是正确的,采取强制手段能达到目的,获益也超过强制本身带来的不便,那么依据功利主义原理,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强制是有害的。我还可以补充一点,这样来表述问题,揭示了密尔先生的“简单原则”其实是个悖论。只有证明除了用于自卫以外,强制本身肯定总是一件坏事,甚至比它能够达到的目的更坏,才能够证明他的“简单原则”是正确的。
……
简言之,所有的经验表明,几乎每个人都既时常需要希望的激励,也需要畏惧的约束,而宗教中的希望和畏惧就是十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尽管有些人过于木讷迟钝,不太把它们放在心上,尽管还有些人时常狂放不羁,只让欲望牵着鼻子走,尽管有些人二者兼而有之。如果有美德是件好事,那么在我看来十分清楚,促进宗教基本教义的信仰也是件好事,因为我确信,至少在欧洲,它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注:这些话对我们重建中华文明信仰体系很有参考价值。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借用别人的话来批驳这种观点。”儒学之所以不是宗教,就是因为只专注于现世,而从不售卖彼岸天堂的门票,在世界思想体系中实属良心过分。因为这样一来,做人就要正视现实,而无法用虚幻的梦境欺骗自己,而这是很多人心理难以承受的。所以儒学舍生取义的勇气是宗教信徒殉教无从企及的,因为儒学清楚自己要付出的是自身的一切,而后者却自以为能用现世的贱命换来幸福的永生,所以任何宗教以及与宗教无异的极权意识形态,本质上都是懦夫,他们就象靠喝酒吸毒才能壮胆的怂包一样,勇气与宗教从来无缘,宗教有的只是靠愚蠢支撑的狂热。同样原因,儒学行善的内核也与宗教信徒有着本质区别,宗教理解的行善是存钱,是交换,总之是与神灵之间一本万利的交易,或是被神灵威逼恐吓下的习惯性被迫,总之都不是自觉自发的行善。而儒学则把行善当成自我完成,是熏陶自身人格。从根本上,儒学是不相信善有善报这回事的,但求无愧于己而已,而并不会对没有回报失望报怨,就象孔子对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的评价,'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不得不说,没有相当强大的内心,很难接受儒学这种极度阳刚的思想。我们普通人,可能只有靠对未来或来世的期盼才能压倒对现实的不满和失望,也都期待付出必有回报,但儒学告诉你:没有来世只有现实,人必须在现实中尽责于家庭和社会,而现实只能靠自己努力支撑,努力也未必有回报,但只要你在这过程中完善了自己,就能自得其乐,无怨无尤。试问几人能做到?没有足够的智力,无法理解儒学,没有足够的人格,无法认同儒学,没有足够的勇气,无力践行儒学。这里要招供,虽然本人自信有能理解儒学的智力和认同儒学的人格,但践行儒学的勇气还差的太远。但这丝毫不妨碍我认同儒学,因为毕竟没卑劣到因为自己做不到,就要对正确的东西反咬一口。我对儒学只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儒学把传授对象锁定于真正的社会精英,而非收高额智商税的忽悠对象,也拒绝提供精神毒品,从而导致低端客户群大量流失。对那些想逃离现实,梦想未来有天堂可去,或有救世主前来拯救自己的人,儒学是暴露自身软弱,让其做不成白日梦的恶人。而对那些收割智商税的形形色色各类救世神棍来说,儒学又是断人财路如杀父母的仇人。所以除了专制怪兽,骨子里反儒学的只有两类:出卖人格换骨头的走狗,甘心被麻醉宰割的牲口。】
密尔先生说:“宗教自由的敌人意识到,对于用惩罚手段去限制反宗教观点的做法,不可能用任何论证给予辩护,因为这也会证明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是正确的。他们迫于压力偶尔会接受这一结果,于是跟着约翰逊博士学舌说,迫害基督教的人是对的,迫害是对真理的严酷考验,真理应该能够经受住也总是成功地经受住了这种考验。”(《论自由》,30/237)密尔先生说,这是一种缺少风度的论证,但它也包含着明显的错误。“真理总能战胜迫害”是个“令人愉快的谬论”。真理并没有获胜;相反,十分温和的迫害往往就足以把它消灭。密尔先生其实是在说,在谴责奥勒留的原则和支持彼拉多的原则之间作出抉择吧!我将尽力迎接这一挑战。
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彼拉多做得对不对呢?我的回答是,彼拉多的首要责任是维护巴勒斯坦的和平,他要对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作出最佳判断,并在作出判断后按此行事。因此,只要他真诚地相信——并且有合理依据——自己的举措对维护巴勒斯坦的和平是必需的,那么他就是对的。承担犯错误的风险是他的职责,即使他违反密尔先生的自由原则,尤其是言论自由的原则。他处在审判者的位置上,他的职责就是冒着犯错误的危险,对带到他面前的人进行公正的审判。
为了证明这种观点,我必须首先思考一个问题:像“正确”和“应该”这些词,在什么意义上能够被用于政府和政治问题?
……
德·迈斯特说过,与所有的酷刑和磨难的迫害相比,逻辑推理对基督教的迫害不知要严重多少倍;此说虽然有些怪诞,却是正确的。
【注:相较于其他一神教,基督教逻辑含量确实高一点。“虽然我向来反感宗教,尤其是一神教的沙漠三教,但三教之间做对比时高下之分还是很明显的。基督教做为最初犹太人教的一个异端派别,可以断然抛弃犹太人的饮食禁忌和割礼等习俗,从而打开了向外广泛传播的大门,这种灵活性和变通能力在沙漠三教中也算出类拔萃了。反过来,伊斯兰的教条则基本完全受阿拉人生活环境和习俗决定。基督教的影响扩大是渐进性,而且长期受打压的,这使得基督教相比初期爆发式征服的伊斯兰教,更注重思辨说服的方式向外传教而非仅依赖刀剑和子宫。以我接触过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前者辩论的逻辑水平完全碾压后者(虽然宗教到最后都只是诡辩)。暴力性方面,基督教也要让伊斯兰教一头,这方面基督教好歹算是伪君子,对作恶还会摭掩,不象另一个完全以此为乐。即便教义有高下,基、伊也是百步五十步的区别。最重要的是,基督教为主的欧洲有古希腊罗马的理性文明资源可供挖掘提炼,无须吊死在基督教一棵树上。在人文精神压倒基督教后,基督教才被迫进行了改革。否则就象埃塞俄比亚也是以基督教为主,与附近伊斯兰地区相比毫无优势。所以本身的灵活变通能力和外在高级文明资源存在二者缺一不可。而这两者,伊斯兰教及集中分布地区无一具备。拿中华文明与伊斯兰社会相比,是对中华文明的一种侮辱。拥有自有的文明升级资源和纯外来影响区别是巨大的,没有自有文明升级资源的伊斯兰社会只有选择做“洋奴”和“义和团”两种极端选择,而已经拥有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学高度理性民主自由内涵的中国人,就根本没有这个问题。从儒学中可以提炼出一切现代文明要素,无须充当洋奴,更无须当愚民。”】
论战也是如此。内战、司法迫害、宗教裁判所以及它们带来的一连串恐怖所构成的冲突,并不比思想战争更加有效,当辩论摆脱了司法惩罚,任何制度、家庭和个人便无法摆脱这种战争了。对受到珍爱的情感的争论、嘲讽和蔑视,对令人倾心的谬说揭其老底,打击或伤害感情,给公众或个人的希望大泼冷水,就像真刀真枪和明确的伤害一样让人恐怖。这种战争的结果是,较弱的观点——不够茁壮、深深根植于感情的观点——被连根拔起,它成长的土地而被化为一片焦土,而昔日的监禁、火刑和杀戮只是击倒了它,环境一变它还会重新生长。打击只会造成一时的受伤或褪色。硝酸盐不会使银器的表面受伤,但会永远改变它全身的颜色。划出一条确定压迫导致痛感的明确界限是不可能的。也许轻轻一触就足以让人警觉。有许多不同的方式足以造成最令人苦恼的伤痛。将某人的观点视为谬论带来的伤痛也是如此。意见分歧可能让人愉快,可能很无聊,也可能引起强烈的痛苦,这痛苦会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其直接原因也多种多样。与某个人有分歧,给他带来痛苦的每一种方式,都是对他思想自由的一定程度的侵犯。让他以某种方式思考会给他造成人为的痛苦,这冒犯了密尔先生的自由原则,除非它是为了自卫,而这种自卫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在我看来,密尔先生的意见自由学说像是贵格会的货色。它好像是在教导人们,无论什么样的报复,甚至其最温和的形式,都是错误的,因为走极端的复仇对社会具有破坏力。
第三章 論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的區分
【注:开篇介绍两派——一派认为对世俗领域和精神领域进行分而治之;另一派认为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区分不在于它们统治着不同的领域,而在于它们采用不同的统治手段。
大众真正的主要动机是个人的算计和欲望。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凡是意欲主宰人类的宗教,必须承认这一事实,诉诸于个人的动机。
【注:学习一神教的内核来重建中华文明信仰体系不能不重视这一点啊!】
第四章 自由學説在道德中的應用
【注:斯蒂芬在下面继续批驳密尔的理论。这里略作记录。】
前面我讨论了密尔先生的原则及其实际应用于思想和辩论自由的理论基础。现在我来谈谈它在道德上的应用。为了避免被误认为无的放矢,也许有必要重述这一原则。“在社会以强制或控制的方式对待个人方面,它具有绝对的主宰力,无论哪种强制使用的手段是法律惩罚形式的物质暴力,还是民众舆论的道德强制。本书的目的在于申明一条非常简单的原则,这条原则就是:人类被允许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对他们的任何成员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就是自我防卫。“接着他又说,”从这种每个人的自由中,产生了个人之间在同样的限制内相互联合的自由;出于任何目的结社自由都不可对他人造成侵害。“(《论自由》,15-16/226)
我们从这条原则中可以合理地得出以下结论。一些人为了串通一气诱骗妇女、大力宣扬通奸是件好事而结成一个社团。他们为此建立了一个出版、传播淫秽小说和小册子的组织,处心积虑地激起年轻人和毫无经验者的欲望。英国的法律会把这种做法视为犯罪。
这类书籍可以称为淫秽言论,为此目的而成立的这种团体可以称为阴谋集团。很明显,密尔先生不但会认为这是错误的,而且,如果报纸态度激烈,他们在谴责该团体时采用的语言比平静讨论这种”人生试验“(《论自由》,81/281)是否恰当时所采用的语言稍嫌过分,那么密尔先生还会视之为迫害。在我国,这种社团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即使国法不管,私刑也绝不会坐视。密尔先生会顺理成章地认为,这提供了一个可悲的证据,证明了我们的褊狭与对真正自由原则的无知。
……
简言之,自由和宽容的真正问题是:争论的目标有什么价值?人人都必须做、必须敢于做并予以忍受的事情——这是无疑会发生的事——是不是他们能够做、能有勇气做和能够忍受的事情;或者,在这种事情中,我们能否有尊严地暂时接受失败,并把握再次尝试的机会?根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把斗争的形式分为两败俱伤的战争和友好的辩论。
这些解释使我可以重申道德不宽容的立法目标,而不必担心受到误解。它的目标是:确立、维护并授权于立法者所认定的良好道德体系或标准。基于已经陈述的理由,我认为,只要这样确立和维护的体系是好的,那么这一目标就是好的。任何特定的体系是好是坏,是一个不可能得出永恒定论的问题;然而我可以说,对人类而言,存在着大量的好事和坏事,尽管其好坏程度无疑有所不同。从立法的实践目标来看,精确的针对性并不那么重要。在任何特定的时代和国家,对这一目的而言,善恶的含义都是足够清晰的。今天的英国流行着许多道德学说,思考者对它们有着广泛的分歧,但这些学说更多的不是与特定的行为是善是恶的问题有关,而是与区分的确切含义、确定特定行为的道德性质的方式以及行善避恶的理由这些问题有关。因此必须承认,抑恶扬善的目标既是可取的,从立法的目的来看也是十分合理的。
这样一来,剩下的问题就只是社会为此目的采取的手段的效用,以及应用这些手段的代价。社会用于抑恶扬善的重要手段有二,即法律和舆论。法律又有刑法和民法。任何一种手段的运用都要服从于特定的条件和限制,用议会法案或舆论的作用使人们从善的智慧,完全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些限制和条件并据以采取行动。
……
英国的刑法确实承认道德,这从以下事实可以得到证明:许多不需要特别列明的行为被当作犯罪,仅仅因为它们被视为极不道德的行为。
……
至于密尔先生的学说,即只有出于自卫的目的,才能运用舆论的强制性影响,我认为这是十分明显的谬论,几乎不必予以反驳。简单一想即可证明这一点。它是一条根本行不通的原则。……
以上讨论的结论是,在许多情况下,法律和舆论确实对道德发挥着强大的强制性影响,其目标在上述意义上是有益的,其手段适合于实现这些目标,付出的代价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过分。果如此,则我认为法律和舆论起着很好的作用,而我不晓得如何能够否定它的前提或结果。
当然,不论法律还是舆论对道德的有益干涉,都存在着一些限制;应该谨慎地遵守这些限制,这在实践中极为重要。这方面的重大原则,尽管不能作出十分准确的表述,但它们数量不多,也很简单。姑举以下数条:
一、无论立法还是舆论,都不应当多管闲事。……
二、无论立法还是舆论,尤其是后者,一旦证据不足,易于造成极大的伤害和极残忍的不公。……
三、在任何情况下,立法都要适应一个国家当时的道德水准。如果社会普遍表达的意见没有严厉而毫不含糊地谴责某事,那么你也不可能对它进行惩罚。试图这样做,必然引起严重的虚伪和公愤。要想进行惩罚,道德上的多数必须占有压倒优势。法律不可能比它存在于其中的民族更优秀,虽然它可以并且能够维护公认的道德标准,可以随着标准的提升而日趋严谨。我们极为严厉地惩罚那些在雅典和罗马几乎不受责怪的行为。也许,有朝一日,对通奸、诱奸甚至乱伦进行惩罚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就目前来看这种前景十分渺茫,甚至可以怀疑我们是否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注:维多利亚时期风气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四、在任何情况下,立法和舆论都应一丝不苟地尊重隐私。
……
规模最大、最令人畏惧的强制——即战争的强制——似乎是为民族提供生存基础的原则之一。它决定着民族能否生存以及如何生存。它决定着人们的信念、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宗教、法律、道德形式和全部生活格调。它不仅是君主的“最后手段”,也是各种形态的人类社会的“最后手段”。总之,它决定着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能够存在多少个人自由。
从这个重要事实中可以得出许多结论,有些我已经有所提及。可以把它们概括为一句话:权力先于自由——自由从本质上说依赖于权力;只有在一个组织良好的、既明智又强大的政府保护下,自由才可能存在。
……
要点是,对这个意义上的自由所表现出的狂热,很难与恰当意义上的服从美德和最广泛意义上的纪律协调一致。不断赞扬现时代,对所谓篡夺的和愚蠢的权威的成功反抗,由此形成的精神态度,几乎必然使人们不承认一个事实:服从真正的权威,顺应真正的必然因素,尽可能从好的方面利用它,是一切美德之中最重要的美德——这种美德是取得一切伟大而持久的功业的要素。如果只是笼统地说说,大家都会承认这一点,然而事到临头,能够意识到按此原则行事的必要性,却是世间最稀少的才华之一。能够认出比你优秀的人,知道应该敬重和服从谁,知道何时反抗不再是荣誉、心悦诚服地认输才是勇气和智慧的表现,都是非常难以做到的事情。善思者在这个问题上无论能够说什么,都起不了多大作用。这种困难,就像凡是具有司法经验的人眼中的那个最大难题一样:一个既有机会说谎也确实有这种念头的人,对于他就一个重要问题作出的直接陈述,如何知道什么时候改信,什么时候不该信?
……
因此,除非我们知道,谁希望做什么,他这样做收到什么限制,出于什么理由解除这种限制,不然的话,对自由的讨论不是走入歧途,就是浪费时间。
记住这些解释,下面我要说的是,民主信条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人类的经验证明了什么,他所证明的就是,把限制最小化,把最大程度的自由赋予所有人,结果不会是平等,而是以几何级数扩大的不平等。在各项自由之中,最重要、得到最普遍承认的自由,莫过于获得财产的自由。如果你在这件事上限制一个人,那就很难看出你给他留下了什么自由。……一切私有财产都起源于劳动并为劳动者带来益处;而私有财产恰恰是不平等的本质。
【注:这里如果区分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就会得到不一样的结论。不过法式自由的基础和英式自由的基础有着显著不同。】
假设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他们十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的劳动成果也被集中在一起,靠这一份共同财产养活。这样一来,你确实为平等和博爱赋予了十分明确的含义,但是你必须绝对地排斥自由。经验证明,这不仅是个理论难题,也是个实践上的难题。它是一切社会主义方案无法克服的障碍,它解释了它们的失败。
能够使共和派的著名设想得以全面实现的、既合理又十分一致的唯一方式,就是把“自由”解释成“民主”。建立一个民主政府,通过平均分配财产承认世界一家,是一个既明确又可以想象的方案,当这种信条得以认真贯彻,而不是一句媚俗的夸夸其谈时,这就是它真实含义。当这样使用自由时,还应加上“不然就是死亡”的说法,以便使这个信条尽善尽美。把“要么实现自由、平等、博爱,要么死亡”这几个词串在一起,并用上述方式进行解释,它们便构成了一种完整的政治学说,实际上十分明确地描述了希望建立的政治体制的本质、它要达到的目标以及使它的命令得以服从所必须依靠的惩罚。这是一种以最激烈的方式表达全部痛苦和怨恨的学说——可以假定,人类中大多数落魄的妒忌者和残忍的复仇者心中,都充满了这种痛苦和怨恨,它所针对的是那些他们视为压迫者的人。只有穷人才会对富人说:通过建立自由——意思是民主——制度,我们现在是主人了,既然人人都是兄弟姐妹,有权平等地分享共同财产,所以我们要剥夺你,不然你就得死。对于这种教义,我们只需说,那些痴迷于共和信条的人最好是扪心自问,他们是否理解其中的缺陷?如果理解了,他们根据什么原则、在哪里划出界线?我想,凡是能够理解这个极其复杂问题的人都会看出,这种信条的解决办法要么太过头,要么根本不是任何解决办法。
【注:从这角度看,斯蒂芬算是能瞥见一点极权主义的兴起的原因了。不过这里民主和共和混用不直到是原文如此还是翻译乱翻的结果,这里暂且存疑。】
对于自由,我已经尽我所言,现在可以做个简短的总结。如果“自由”有任何明确的含义,如果始终从这个意义上使用它,那就几乎不能作出真正具有普适性的论断,更不可能将它视为好事还是坏事。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仅仅以普遍流行的方式使用它,没有赋予它任何确切的含义,那么你很容易随意对它作出任何一般性的论断;但是由于这些论断没有确切的含义,它们既无法作为证据也无法作为反证。因此,“自由”一词要么误导人们诉诸激情,要么具体表达或暗含着一种极复杂的论断,只有通过详细地研究历史才能证明其真伪。……
这有点儿像狡辩,但是我相信,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缜密思维的首要条件之一,即对基本概念的准确定义,就可使其成立。人们有一种几乎无可救药的倾向,他们用自己的偏见为语言打上烙印,从而使那些与他们有利害关系的所有重大问题受到扭曲。在许多情况下,法律不仅是命令,而且是善意的命令。自由不是指完全不存在限制,而是指不存在有害的限制。 正义不仅意味着将普遍规则公正地用于具体案例,而且意味着将善意的普遍规则公正地用于特定案例。有些人自觉不自觉使用“正确”一词同时指正确和有益。诚然,使语言变得绝对中立和没有感情色彩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除非认识到它的模糊性,否则思想的正确也就无从谈起,而且造成的伤害与受误导者的逻辑能力、一般精力成正比。
【注:后面用密尔和revolution这个词的关系揶揄了下密尔。这也可算是个知识分子“胡说八道”的典型案例了!】
第五章 平等
我要考察的现代信条的第二个重要条目是平等。在构成这种信条的三大教义之中,平等最有声势,同时也最模糊。它可以指人人应当平等服从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律,也可以指应当公平执法。它可以指社会的全部收益、人类征服自然的全部收获,应该集中于一个共同库房,并且应该在人们中间平等分配。它也许仅仅反映着——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如此——无产者对有产者的妒忌,反映着他们对一种人们的差异不像现在这样大的社会状态的朦胧渴望。所有这些想法都是含糊不清和不充分的,很难归纳成确定的形式加以讨论。反驳一种情感是不可能的,除非只是重复一些常识,而对于这些常识,认为其缺少说服力的人不太可能相信它,已经相信的人又不需要它。
【注:结合“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看,有种不可言说的红色幽默。。。下面先批驳了边沁的《道德和立法原理》,然后主要批驳了密尔的《功利主义》第五章“论正义和功利的关系”和《论妇女的屈从地位》全书。】
为了证明或解释这一点,我可以引用《论妇女的屈从地位》全书,我不赞同这本书里从头到尾的每一句,但这里我将只从平等这个特定话题的角度来讨论该书。平等大概是当今时代最强大的感情,在我看来它也是最低贱、最有害的感情,就我所知,密尔先生的著作则是对这个题目最为清晰的说明。
密尔先生这本书的目的是对以下观点的理由作出解释:“调整两性之间现有社会关系的原则,即女人从法律上服从于男人,从本质上是错误的,目前它是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它应该被完全平等的原则所取代,这一原则既不承认一方有任何权力和特权,也不承认另一方缺少能力。(《论妇女》,119/261)
……
结论是,”妇女在社会中的屈从地位,成了现代社会制度中一个孤立无援的醒目的事实“,它与”现代世界所夸耀的进步运动“”截然对立“。这个事实引起了一个与之相对的”初步假定“,它”大大压倒了在这种环境下习俗和惯例所产生的任何对它有利的假设“。(《论妇女》,137/275)
……
可以把他的理论概括为以下观点,我认为前面引述的话要么对它们有所暗示,要么可以归纳出来:
一、正义要求全体人民应作为平等的人生活在社会里。
二、历史表明,所谓人类的进步,就是从”强制性法律“到命令和服从成为例外的进步。
三、在我国和其他一两个国家,”最严厉的法律“在人类生活的其他所有关系中已被”完全废止“,可以假定它也不适用于两性关系。
四、有关这种关系之性质的众所周知的事实表明,在这件特定的事情上,上述假设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
我不同意这些观点中的任何一条。先来谈谈第一条主张,即正义要求全体人民应该作为平等的人生活在社会里。我已经说过,它与以下主张是一样的:全体人民作为平等的人生活在社会中是合宜的。这能够得到证明吗?它显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主张。
我想,如果法律创设的权利和义务是普遍有益的,它们就应该适合于享有这些权利、遵守这些义务的人们的境况。它们既应该承认实质性的平等,也应当承认实质性的不平等;对他们应该进行改造和修订,以便总是公正地反映社会现状。总之,政府应该适应社会,就像人的衣服要合身一样。当人们不平等时,却要用法律创造假定他们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无异于削足适履。毫无疑问,或许有必要为消除社会罪恶或保护社会免于特定的危险或弊病而立法。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就像外科手术,它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或可比喻为有时为支撑脆弱的四肢或将它固定在特定位置而安装的构件。然而这不是正常状态。权利和义务的形成应该像衣服一样,应该保护和维持社会的自然状态。因此,”正义要求人们作为平等的人生活在社会里“这种主张,可以理解为:”法律不应当承认人们之间的任何不平等,因为这不符合合宜原则。“
在我看来,它包含着如下主张:”人类之间的任何不平等,其重要性都不足以影响合宜地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我完全反对这种主张。我认为,存在着许多差别,其中一些比另一些更持久、在范围上更广泛,也有一些是如此显著和重要,除非人性彻底改观,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废除它们;在这些差别当中,年龄和性别的差异最为重要。
……
此外,这种契约也包含着弱者对强者的顺从。在我看来,它的证据就像欧几里得定理一样清楚。具体论证如下:
一、婚姻是一项契约,其主要目的之一是家庭的治理。
二、这种治理必须通过法律或契约,由婚姻的一方授权另一方。
三、如果这种安排是由契约作出的,有违契约的现象只能由法律给予救济,或按契约双方的意愿解除伙伴关系。
四、在这种案件中法律无法提供救济。因此违反契约的唯一救济手段,是婚姻的解除。
五、所以,要想让婚姻持久,必须把家庭的治理权通过法律和道德交到丈夫手里,因为没有人会提议把它给予妻子。
密尔先生完全没有能力对付这种论证,而且他显然会接受另一种选择,即应当让双方随意解除婚姻关系。他对契约做了一番在我看来不啻是幻想的论证之后,他又有如下高论:”事情绝不可以成为一方权力无边,另一方只有服从,不然这种结合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双方从中解脱出来就是一件幸事。“(《论妇女》,157/292)
在我看来,这是彻底误解了家庭治理的性质,误解了可以提出夫妻之间服从与权威问题的事情,没有人会主张,男人应当由权力像对待奴隶那样命令妻子,她若不听话就可以拳脚相加。以法律的眼光看,这种行为是残忍的,足以构成的离异的理由。服从问题的出现与此完全不同。它会在最相亲相爱的夫妻之间产生,而且无疑也经常如此,对恩爱夫妻不需要干预,就像船长与他的大副有着绝对的友谊和信任,不需要他的绝对权力插手其间一样。
……
概言之,在我看来,规范两性关系的所有法律和道德应该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上:它们的目标是为男女这两大类人提供共同利益,他们通过最亲密最持久的纽带结合在一起,除了一个团体内部不同成员的冲突之外,他们不可能有真正的利益冲突,但在各种形式的能力方面,他们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平等的。
法律和道德已经用一夫一妻制、建立在妻子服从丈夫基础上的不可解除的婚姻,与行为、习惯和服饰差异相对应的劳动分工等,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种解决方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我要坦率地承认,在许多具体事例中,强者在这种关系中会滥用权力,就像在其他许多事情中一样;他会把规则制定得对自己有利,而这规则其实给双方造成巨大伤害。没有必要详细说明那些关系婚姻对财产之作用的法律的无聊,这种法律很容易被一般的合法婚姻协议所取代,它类似于谨慎的人在必要时做出的安排。至于对妇女施暴的行为,要使这类法律尽可能严厉,只要不致其失效即可。而向妇女开放一两个目前将她们拒之门外的职业,这只是个情感问题,没有多少实践意义。这里我无须重启迂腐无聊的讨论。我现在的目标只是肯定一种普遍现象,即男女之间是不平等的,涉及两性关系的法律应该承认这个事实。
【注:下面接着反驳二、三两条目。这里不赘述具体过程。】
强制是任何法律的绝对本质性的要素。其实,法律不过是特定情况下针对特定目标实施的强制。所以,废除强制性法律,不可能意味着从法律中剔除强制性要素,因为这将彻底毁灭法律本身。
密尔先生论证的语气表明,他所说的”强制性法律“和”最严厉的法律“,是指不受任何法律制约的强制。如果这就是他的意思,他应当把它说出来;然而他一旦说出来,立刻就会陷入与事实明显矛盾的境地,因为现代欧洲的婚姻制度绝非是一个不受强制性法律调整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法律以最严厉的方式管制人类最强烈的激情。
……
具体而言,出身好、教养好的人,父母优秀,谨慎而本分,家境殷实,遗传给他们健康的头脑和体魄,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和那些出身贫贱、教养不良、父母没有什么见识传授给他们,也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他们的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平等可言?诚然,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太多名份上的不平等了。
【注:诚然,受限于基因组成和投胎环境,任何人都不同,也就不可能实质上的平等。】
概括来说,我认为,平等和正义没有任何特殊关系,除非是指狭义的司法公正;在社会生活的大多数重要关系中,无法肯定平等是合宜的。历史没有证实下面的观点:在漫长的时间里存在着持续的进步,其大方向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差异。尽管它的确证实了这样一种观点:人们之间天生的不平等的表现方式,以及产生结果的方式,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它倾向于通过个人订立的契约而不是公共权力为固定人们之间的关系而制定的法律发挥作用。
下面我谈谈”平等“一词的其他含义中最重要的内容——政治权力的的平等分配。这大概是能够赋予”平等“这个模糊概念的最明确含义。……几乎所有的报纸、大多数现代政治思想著作,都以类似于宗教的狂热看待民主的发展和即将到来的普选权。对于这些我是一概反对的。
首先,应该恰当地指出一种区别,尽管它相当清楚并且极为重要,却不断被人忽视。按你们的意志去立法吧,倘若你们认为恰当,就把普选定为不容反抗的法律吧。但你们离平等仍然像过去一样遥远。政治权力的形式变了,其实质却未变。将政治权力切成碎块的后果,无非是让那些能够赢得最大多数碎块的人去统治其他人。这样或那样的强者永远进行统治。若是军事政权,造就伟大军人的品质会使他成为统治者。若是君主政体,国王在大臣、将帅和官员身上所看重的品质将带来权力。而在纯粹的民主政体中,统治者将是那些操纵玩偶的人及其朋党;但他们与选举者之间的平等不会大于君主政体下军人或大臣与臣民之间的平等。政体形式的变化更多地改变了上层的状况,而不是它的实质。……
简言之,政治权力的划分更多地与自由而不是平等有关。它是好事还是坏事的问题自有依据,必须直接参照它的效果才能决定。这种效果繁多而复杂,试图全面描述它们或对它们的性质作出全部说明,无异于白费心思。我希望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其令人不快而一直受到忽视的一点——我们所了解的广受欢迎的制度,不论有何强势的一面,它们也都有弱势和危险的一面,不配得到它们的进步引起的那种盲目崇拜和一致赞美。
……
对于普选的理论与实践的缺点,我的看法的要点是,我认为愚智之间有着真实而自然的关系,普选权则倾向于颠覆这种关系。我认为,聪明善良的人应该统治愚蠢而恶劣的人。如果说,聪明善良的人唯一能发挥的作用就是劝诫他们的邻居,应该一视同仁地允许每个人为所欲为,应该以选票的形式让他们分享一定比例的主权,这样做的结果是智慧引领权力,那么在我看来,在那些曾让相当多的人陷入的想入非非之中,这算是最疯狂的一种。
……
我当然不同意密尔先生的看法,他认为英国人普遍愚钝,缺乏创新精神,彼此之间十分相像,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桶鲱鱼一样。
【注:崇拜密尔的洋奴看到密尔对英国佬的评价会不会破防呢??😀】
我本人的观点是,能够以连贯系统的思想从事一件事的人,或能够把握某个包含着诸多因素的问题的影响人,总是极少数。我还应该补充说,要想真正做好统治一个伟大的民族这项工作,需要大量特殊知识,需要坚定、有节制和冷静地运用这个国家各种最优秀的人才。
……
平等,就像自由一样,在我看来虽然享有盛名,内容却贫乏得很。我认为,近来对它的狂热主要归因于两种环境:大革命之前法国特权阶层令人厌恶的地位,美国财富的巨大增长。……
……
总而言之,我认为对于平等我们所能说的少数几句真话就是,人类事实上是不平等的;但们在相互交往中应该承认存在着真正的不平等,就像承认存在着实质性平等一样。他们既倾向于夸大真正的差别,这是虚荣的表现;也倾向于否则其存在,这是妒忌的表现。这两种夸张都是错误的,而后一种错误尤为卑劣和懦弱,属于弱者和心怀不满者的错误。对存在着实质性平等予以承认,仅仅是为了避免犯错误,这并不影响那些公认为平等的事物的价值,并且这种承认通常是朝着内在不平等迈出的一步。如果平等地禁止任何人犯罪,人人都要信守契约,冷静、有远见和明智的人就会胜出,轻浮、放纵和愚蠢的人就会失败。由此可见,平等是一个表示关系的词,自由与此不同,自由是一个表示否定的词。平等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除非我们知道哪两种或更多的事物被确认是平等的,以及它们的本质是什么,当我们对这些要点有了了解之后,我们得到的只能是关于事实问题的陈述,不管是对是错,也不管重要与否,它是事实本身。
【注:结合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几大一神教教义说,一个教主统治着一群信徒就是最接近”平等“的时刻,尤其是当它们都下地狱接受最后审判时尤为如此。】
第六章 博愛
现在我来考察民主信仰三教义中的最有一条——博爱。在某些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人们相互怀有良好的愿望和相互帮助是一件好事,这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常识。同时我也不得不想,许多人和我一样,看到或听到博爱的大话时会感到厌恶。这种爱经常是一种无礼的干涉。……我在读卢梭的《忏悔录》时发现,几乎很少有文学作品能像他对人类表达的爱那样让人恶心。”你把爱留着自己享用吧,别用它来烦我们!“这便是他的书总让我想到的评语。……在我看来,法国人爱人类的方式,是他们众多最不可宽恕的罪恶之一。能够要求于绝大多数人类的,不是爱,而是尊重和正义。……
【注:对极权主义思想头子之一的卢梭的评价还是很贴切的。】
有关崇拜和献身于抽象的人道精神的教诲,有着多种形式。我打算考察的形式可以在密尔先生的《功利主义》中看到。它也具有密尔先生所有著作的优点,表述得极严肃、极清楚、极有分寸,使我了解了民众情感的教条形式。下面是密尔先生阐述其学说的一些话,它们分别见于《功利主义》二、三、五各章:
我必须再次强调,功利主义的反对者们很少正确认识到:在功利主义理论中,作为行为是非标准的“幸福”这一概念,所指的并非是行为者自身的幸福,而是与行为有关的所有人的幸福。因为行为者介于自身幸福和他人幸福之间,故功利主义道德要求他做到如同一个无私的、仁慈的旁观者那样保持不偏不倚。在拿撒勒人耶稣的“黄金律令”里,我们读到了完整的功利主义伦理的精神——“人如何待你,你也要如何待人”、“爱邻如爱己”,这些思想构成了功利道德的理想境界。作为实现这一理想的最佳捷径,功利主义要求首先法律和社会安排应当尽可能地让个人的幸福或个人利益(按照实践说法)与全体利益趋于和谐;其次教育和舆论对人的性格塑造具有重大影响,应当用这股力量在每个人心中建立起自身幸福与全体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自身幸福与按照普遍幸福行为模式(包含正反两方面)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之间的联系。如此一来,个人就不可能产生只顾自我的幸福观,其行为就不会与普遍的善相对立,而且每个人都养成一种习惯性行为动机去直接促进普遍的善,而与之相关的感情也会在每个人的情感生活中占据突出的位置。假如功利主义伦理的抨击者们能将这些内容的真正含义呈现在他们的头脑里,我不知道他们可能坚持的其他伦理还能对此提出何种更好的建议?还有别的任何道德体系能够让人性得到比这更美好更崇高的体现么?或者那样的道德体系除了基于功利主义的原理之外还能依赖于什么样的行为动机来实现它们的教义?
【注:这里有点繁琐,意义也不大,不赘述。”爱邻如爱己“这出自《新约·马太福音》5。从这点能看出某些洋奴分辩”博爱“和”兼爱”实属搞笑。这种“博爱”实质上就是兼爱,而真正的博爱叫做仁。韩昌黎《原道》:“博爱之谓仁。”】
首先,我确实不同意密尔先生对功利主义标准的陈述,即“不是当事人自己的幸福,而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用边沁的话说,“一视同仁,无人例外”,尽管密尔先生又为它补充上了限定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本人也是功利主义者。也就是说,我认为从事情的本质来看,必须提出某种可以用来检验到的原理的外在标准;幸福就是一个可以用于这个目的的最重要、最不易引起误解的概念。它也是为了获得唯一支持有可能诉诸的目的。公然宣布在任何意义上都与这个概念无关的道德体系,不过是一种任何都不会关注的智力游戏。如果不把合宜——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作为基础,我不知道怎么有可能讨论道德法则或法律规章的价值。
……
总之,立法者视为其法律标准的幸福,是他对法律对象的愿望给予他认为适当的重视之后,他希望他们拥有的幸福,而不是他们希望拥有的幸福;道德学者的情况更是如此。立法者总是有义务对法律对象的愿望予以最大的关注,尽管在特定情况下他或许能够反对、抵制有时甚至改变它们。道德学者必须完全依靠劝说,所以他不受这种限制。如果他对自己的观点信心十足,或者他不在乎别人是否接受它们,那么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将自己的学说建立在一种幸福观之上,它不同于他的时代和国家流行的观点,但它往往并不是最没有影响力的学说。个人的缺陷是使法律成为可能的条件之一,与此相似,自觉的无知也是道德体系拥有权威的一个重要来源。人们意识到自身的缺陷和无知,同时他们也觉得,生活在没有任何行为规则或准则的状况下,像我们所设想的动物那样,纯粹受一时冲动的引导,这在道德上是不可能的,这种感情促使他们接受那些声称拥有权威者为他们作出的规定。如果人人对自己的头脑了解得一清二楚,道德说教就派不上多少用场了。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我应当将密尔先生的学说修改如下:功利主义的标准不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如果幸福是一个像身体健康一样清晰的概念,倒是可以这样说),而是设立标准者所形成的理想的最大可能扩张。……
……
然而,除此之外,无论是立法者、道德学者还是其他什么人,关心他们自己和亲戚朋友的幸福要远胜过关心别人的幸福。密尔先生好像认为,“严守中立,做一个无私而仁慈的旁观者”(《功利主义》,218)是不言自明的头号真理。果真如此的话,那我只能说,几乎所有人的全部生活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非正义过程,因为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都在为自己以及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提供幸福的手段,根本不去考虑其他人。不仅如此,由人性所定,个人动机和社会动机是分不开的,不是分别存在的。我们想给别人带来快乐,是因为使他们的快乐能让我们开心。……
【注:从斯蒂芬的反驳话语也可以看出这种“博爱”确实就是兼爱。】
自爱(self-love)是人类之爱以更广泛形式传播的基础,是善行的终极基础,我认为,我前面引述的论述功利主义道德之终极约束力的全部文章,都承认这个事实。我和密尔先生的分歧在于,他相信这种对自己和朋友的自然情感会逐渐改变它的性质,最终升华为一种及于世界的大爱;这种形式的爱能够形成一种新的信仰,对于这一信仰我们唯一需要担心的是,它有可能过于强大,不利于人类的自由和个性。
【注:斯蒂芬认为道德依赖于宗教,这点和密尔的观点有显著差异。】
简言之,密尔先生的学说是,文明的进步将使人们产生强烈的普世之爱,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具有宗教性质,发挥比所有现存宗教更大的影响。
【注:如今,起源于这种思潮的马教确实是影响最大的一神教。。。】
有这种想法的人的预期,会对没有这种想法的人产生独特的影响。如果世界普遍接受了这位理论家的人生观,他们看起来会喜欢关于世界应是什么样子的很多理想版本。普世之爱,奉献于所有人或普世主义,等等,不过是对某种得势的手段论的迷狂,通过这种手段,可以把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他们的存在满足了理论家的假想癖)带入理论家称为幸福的状态。一个人的思想感情,他对现状的评估以及他针对现状采取的行动,只要真沾染上了这种理想,那么正如经验一再表明的那样,他通常会为了他本人所理解的后代的幸福,毫不犹豫地牺牲现在活着的人所理解的幸福。去世,他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自己,或者说超越了自己。同情别人,关心别人的事,对自己眼中别人的错误行为难以容忍,这些动机在他身上确实变得比在其他人身上更为强烈,更加有力地影响着他的行为,但是这种事本身并不是优点。它肯定没有赋予任何人得到别人信任的权利。
【注:这段话结合如今左衽猖狂的嘴脸尤其是环保主义者的表现,斯蒂芬确实有先见之明!】
正如我已指出的,最令人厌恶的事,或者说,在很多情况下最严重的侵害,莫过于你不想得到其爱的人所表示的爱。每个人都最大幸福,是他能让自己觉得最幸福,这要由他本人也只能由他本人来判断。
【注:在接下来的两段中,斯蒂芬主要强调地球人几乎没有一致的利益,地球人之间绝大部分情况下不是兄弟姐妹,一般也不沾亲带故。冲突才是主旋律。不过这个翻译把堂吉诃德称为道学家,真是个SB行为!这里不再赘述。】
一个从他自身以及他与别人的明确关系出发的人,是不会为这些问题苦恼的。这样的人会满足于少管闲事。他可以说:“我希望过得好,我希望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过得好;我关心自己的国家;跟我有缘的各种人,我也会好好待他们;但是,如果在我的人生旅途上有哪个人或团体把我和我所关心的人当作敌人对待,那我也会把他当作敌人对待,至于我们能否从亚当或类人猿那里找到某种关系,我绝不会在乎这种问题。告诉我某个人做的某件事,我就能告诉你他是我的朋友还是敌人;但是,不加区分地把地球人统称为我的兄弟姐妹,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我十分看重真实的人际关系,是不会把这么动情的称呼送给那些人的,因为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而且说实在话,我根本就不关心他们。”
【注:斯蒂芬作为基督徒,居然不爱自己在其他国家的教友,这有点不基督了。。。当然这也可能是在讲爱教友,不爱异教徒。。每个人应该先爱他自己———然后才是家庭——祖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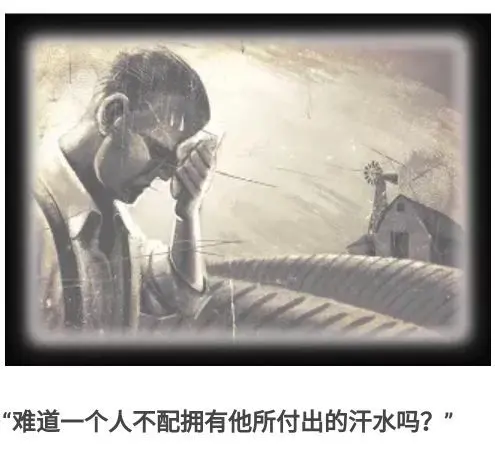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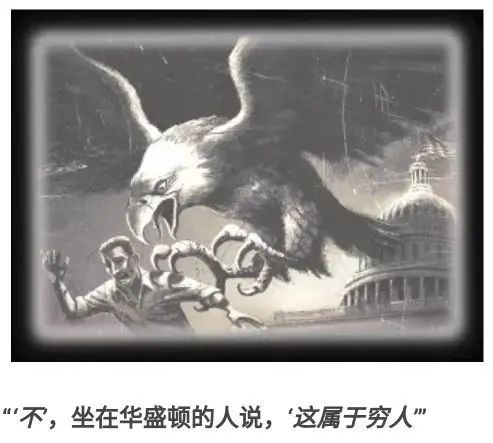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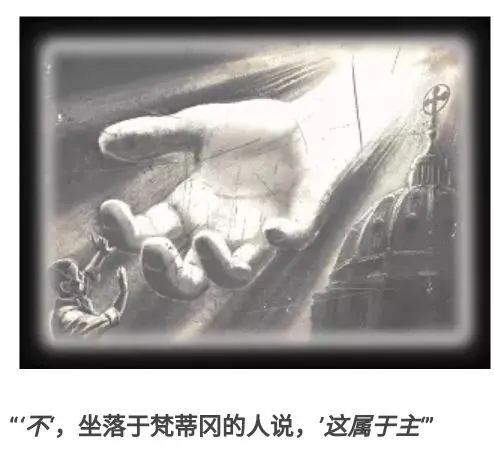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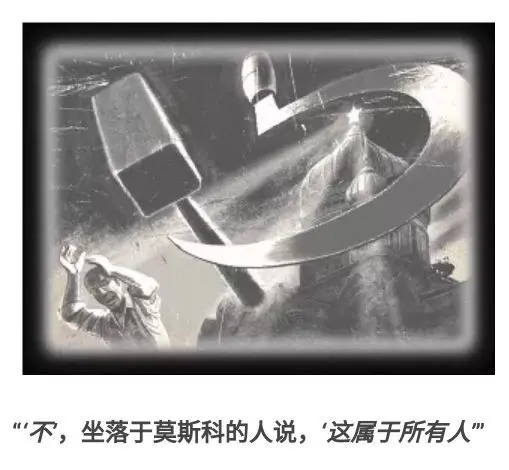
【注:不不不,这属于我。】
【注:至于虚无缥缈的全人类,全灵长类,全哺乳动物,全脊椎动物—————让脑子出毛病以至于精神错乱的左派分子去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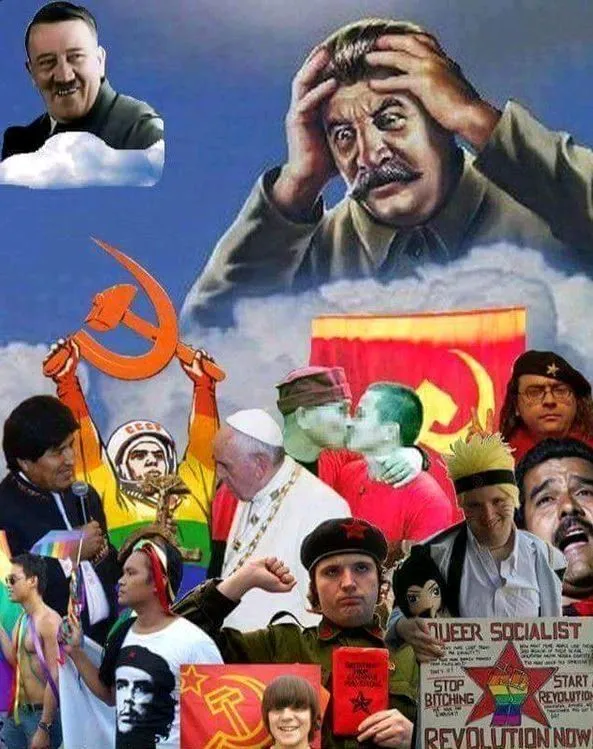
相信博爱宗教的人是不能这样说的。他必须去爱全人类。如果他想让我也那样做,他必须给我一个理由。然而,他通常不仅不给我理由,还全面否定唯一可能的理由——耶和华创造了人类,并要求他们彼此相爱——的真实性和恰当性。这个理由是否属实是一个问题;然而我不能理解的是,没有这种信仰,如何能够主张让人们彼此相爱?需要有能够想象的最为清晰的神启,才能使我作出尝试,去爱那么多根本不必提及的人,或是去动情地关心那些跟我毫不相干的大众。
这就是我有以下看法的理由:博爱的性质存在着大量的自欺;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的希望对全人类表示无限同情的朴素感情,不值得给予人们经常要求给予它的赞扬。
……
所有这些讨论的一般结论是,博爱,单纯的普世之爱,从本质上不适合成为一种信仰。也就是说,它不适合控制人类的能力,为它们提供指导,与其他能力进行比较之后为一种能力指定一个位置——而如果没有这种干涉,它就没有这样的位置。
……
以下是宗教的要点,我表述得尽可能笼统,但仍然具有足够的精确性来表达我的意思。
一、使徒教义中所说的话都是真理。相信他们,并根据它们实行自律。
二、神是存在的,穆罕默德是神的先知。要按照穆罕默德的吩咐做事。
三、一切实在都是罪,如果你头脑清醒,就应当希望摆脱它们。某种人生过程会使你快速摆脱实存的苦难。
四、至上全能的神为你们全体指定了等级,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的人生规则。你们若不按自己的等级规则生活,将受到各种方式的可怕惩罚。大自然也充满无形的力量,他们或多或少都与自然目标相关,它们必须受到崇拜和尊敬。
这便是宗教一词的原义。以寥寥数语表达的这四种教义中的每一种,在本质上都是完备的。它所陈述的主张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但是,如果它是正确的,它便为人生提供了完备的实践指南。
【注:这对我们重建中华文明信仰体系很有参考意义。】
还必须牢记在心的是,基督教固然热烈表达着温柔仁慈的情感,但它也有令人恐惧的一面。基督教的爱只是一时的,是有条件的。它会在地狱门口停下来,而地狱则是整个基督教学说的本质部分。
【注:用地狱恐吓人才是基督教学说的本质部分,作为异教徒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历史的事实是,如果基督徒的含义是只把四福音书中的博爱语言作为人生唯一的完备指南,那么没有任何一个规模可观的人类团体是、曾经是或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以冷酷而真诚的态度把世界翻个底朝天。他们将是一批热情的共产主义者,摧毁一切公认的行为准则,和人类制度。
【注: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基本上都是基督徒,这点是符合事实。马教主、斯大林、恽代英等都是如此。有一说一,血腥黄暴程度远超《我的奋斗》的《新旧约全书》本身矛盾重重,前后理念差异很大。】
第七章 結語
对于前一章阐述的学说,可以作出如下正面表述:
一、管理和引导人类的全部生活,有赖于对是否存在神和来世这一问题的回答。有神而没有来世,神对我们便毫无意义。有来世而没有神,关于来世我们便不可能形成任何理性的推测。
二、如果既没有神也没有来世,理性的人就只能要么用他们的喜好,要么用普通功利主义来规制自己的行为。
三、如果既有神也有来世,理性的人就会用一种更宽宏的功利主义规制他们的行为。
四、不管人类用什么原则规制他们的行为,“自由、平等、博爱”这句话所暗示的思想体系,都没有为他们表现出合理的热情留出空间,因为不管采用什么原则,总是存在着人们不应享有自由的大量事情,他们从根本上说是不平等的,他们根本不是情同手足的兄弟,或只在特定条件下才是这样,而这些条件会使博爱的主张变得微不足道。
进行得出这些结论的思考,就不可能不问一句这些结论有怎样的重要性。我上面讨论的问题,已经以各种形式争论了上千年。这是否与它们终将获得解决的可能性相称呢?如果不相称,那些对永无尽头、周而复始、不断使人间烽烟四起满目疮痍的冲突不感兴趣的人,何必要去争论它们呢?
答案是这样的:这些思考也许永无止境,它们的结果多是破坏性的,然而它们大有用处,而且确实必不可少。它们能够证明,一组特定的意见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恰当地说它们根本不是意见,这种思考可以揭示特定的观点是相互关联的。
附錄一 功利主義筆記
【注:下面的内容是斯蒂芬在《蓓尔美街报》上发表的两篇讨论”功利主义“问题的文章概要。
一切道德争论都可以归结为四个问题。第一,道德的范围是什么,它们涵盖人生的哪个部分,它们假定人性中存在着其他哪一些要素?第二,善恶之分的本质是什么?第三,我们如何确定特定行为的善与恶?第四,我们为什么应当趋善避恶?
……
在古罗马时代,那些很少或几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中间,也有大量的道德观,但它整体特征不同于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道德观。哪一种道德体系最好,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下面的问题:是异教哲学家还是基督教传道士对事实作出了正确的评价。……一种行为的正当性,归根结底取决于人们对事实问题所能形成的结论。
附錄二 第二版前言
【注:这里主要是对最重要的两位评论者,约翰·莫利先生和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先生做一些回应。】
教士实行统治的重要手段不仅是借助于天堂和地狱、个人的愿望和恐惧,而且借助于各种各样的愿望和畏惧、同情和反感,它们都依赖于并且关系到未知的来世。这些愿望和畏惧、同情和反感对人们的现世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就像法律对他们的影响一样,从这种意义上说,宗教和法律都是世俗的。它与法律的不同之处在于环境,即它的终极基础是它的劝说对象的情感。这些情感是由外在于宗教和法律的因素决定的。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年代,这些因素的力量也各不相同。教士采用的手段也不同于立法者的手段,一方面,在它完全发挥作用的地方,它更微妙,也更强大,另一方面,它在所有情况下更不明确,适用范围更不具有普遍性。
文獻舉要
1.斯蒂芬的著作
2.研究文献
注釋
譯後綴語
【注:这里冯克利先引用了海德格尔的话“语言乃存在的家园。”讲翻译工作的困难(难以完全准确翻译文章。然后下面为了证明这一点,主要讲了两个例子:Liberty早期常以复数形式出现;西班牙中餐馆和tortuga。】
这件因语言差异而来的尴尬事,或可作为海德格尔“语言乃存在的家园”的一个生动笺注。海氏的学问深奥得不得了,满篇都是对现代技术世界里如何重构生命价值的终极究问,中土大多数人的实存主义当然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境界,只是标举“敬鬼神而远之”和“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为人生鹄的,有一点儿价值关切的人,顶多再加上一句“割不正不食”。
【注:冯克利顶礼膜拜重构生命价值的终极究问的海德格尔,跟崇拜黑格尔那种更能重构终极生命价值的邪教头子有什么区别????还有脸嘲讽”中土大多数人的实存主义“。这不是妥妥是反人类的”宏大叙事“,一点不关心人间情况,人生价值各有不同,谈何终极究问?这种终极究问本质上不过是一神教教徒面对末日审判的迫近而想出的终极”献祭“。。。。此外全书很多内容充满了满满的后现代主义的毛病,这显然就是其破四旧的”成果“,比如冯克利分不清天下和世界的区别,还把堂吉诃德称为道学家等。。。】
The Liberty of Ancients Compared with that of Moderns
Congressional Government: A Study in American Politics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The Road to Serfdom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The Law of Liberty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极权主义的起源——经济人的末日
- 简介
- 中文版序
- 西元1994年版序
- 西元1969年版序
- 前言
- 第一章 反法西斯主義的錯覺 The Anti-Fascist Illusion
- 第二章 群眾的絕望 The Despair of The Masses
- 第三章 惡魔再現 The Return of The Demons
- 第四章 基督教教會的落敗 The Failure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 第五章 極權主義奇跡?——以意大利和德國作為實例 The Totalitarian Miracle: Italy and Germany as Test Cases?
- 第六章 法西斯主義下的非經濟社會 Fascist Noneconomic Society
- 第七章 是奇跡,還是海市蜃樓?Miracle or Mirage?
- 第八章 未來:東西對抗?The Future: East Against West?
- 附录:极权主义的表征
- 把个人利益同人民的利益相结合
- MSA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简介
英文名: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Author: Peter Drucker
评论:作者显然对极权主义的产生存在误解,不管过去的实践,而就现代社会而言,苏联社会显然比纳粹德国社会更早建立更强的极权主义社会。纳粹德国本身就是为了打击布尔什维克的入侵才建立的,故而纳粹德国的的病态程度不会比苏联更高。
中文版序
这本书对丘吉尔影响很大,丘吉尔在西元1939年春天称它是“唯一一本了解并解释两次大战间世界形势的书”。
【注:虽然当时德国还没闪击波兰,丘吉尔就看到了和德国的大战。这本书为丘吉尔决定和苏联勾结一起打击德国提供了精神支持。丘吉尔一心想要维持的大英帝国被自己养起来的美国和苏联给肢解,也算遭到报应。】
《经济人的末日》始终是唯一一本非叙述“历史”,而是从社会和政治层面来分析西元20世纪前二十五年之欧洲和欧洲社会的著作。
【注:其它人对极权主义的看法或许和经济人扯不上关系,但是彼得·德鲁克把极权主义和经济人联系到一块,确实是个创见。但是经济人的影响却并非其所声称的那样,实际上,洋人的两大精神祖宗——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古希伯来耶稣。但亚里士多德是反商业的,它对属于货殖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采取否定的态度,虽然当时应该还没有资本这种词。另一个精神祖宗耶稣也强调“富人能上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有些洋奴说这富人是特指,也是为了洗地无所不用其极。正如文化马克思主义作用下的女权分子说男人都该死一样,确实不一定是指地球上所有男人都该死,但中国男人肯定该死。结合后来第二一神教和第四一神教统治下对商贩的迫害和歧视的现实情况以及第三一神教对Kafir征收重税迫使Kafir改宗,经济原因是极权主义流行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孔子孟子都重视商业发展,还有子贡这种富甲一方的贤人,这也使得我们中国人能长期葆有自由。一百多年来,我们和三大一神教都交过手,最终还是被第四一神教教徒给奴役了,几乎失去了一切。亡天下于一神教,连亡国奴也当不了了。未来的前景也不客观……】
西元1994年版序
德鲁克认为本书被刻意忽略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政治正确”。它不符合战后政治两种广为接受的观念:一、纳粹主义Nazism纯属“德国”的现象,只能从德国的历史、民族性等德国专属特性去解释。二、马克思主义者将纳粹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垂死前的挣扎”。然而本书却将纳粹主义于极权主义视为全欧洲的疾病,纳粹德国尤为极端也最病态,与斯大林主义Stalinism相较并无明显不同,也好不到哪去。比方说,反犹太主义就并非滥觞于德国,而是首见于西元1890年代法国的德雷夫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中一连串迫害和大规模煽动的行径。《经济人的末日》亦主张,造成“群众的绝望”并使他们轻易成为极权主义迫害及恶魔论之祭品的,是马克思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失败,因为它无法成为群众的信条及救世主。
【注:德雷福斯事件(法语:Affaire Dreyfus,或称德雷福斯丑闻、德雷福斯冤案是西元19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一宗政治事件与社会运动事件,事件起于西元1894年一名犹太裔法国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误判为叛国重罪,在当时反犹氛围甚重的的法国社会,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和争论。争论以西元1898年初名作家左拉投书支持德雷福斯之清白为开端,激起了为期十多年、天翻地覆的社会大改造运动(西元1898-1914年)。这固然是反犹太主义的表现,但是这是一千多年来基督教社会迫害犹太人的海量事件中不严重的一起。实质上来说,第二一神教、第三一神教和第四一神教迫害犹太人都平分秋色,不相上下,习惯就好。希特勒和斯大林惺惺相惜,互相学习,当然算一丘之貉。显然,斯大林更邪恶一些,而不是德鲁克认为的那样。因为德国的人才基本上还在,俄国的人才快被屠光了。现代德国还是欧盟老大,而俄国已经沦为二流国家了只能靠儿子续命了。】
研究这个主题的模板,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西元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她将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崛起归咎于西元19世纪初级德国的体系型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或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注:阿伦特显然从另一个视角为我们揭示了极权主义的起源,正如其所说“极权主义本身就是要消灭自由本身”,虽然极权主义的一大代表——马教主张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现代著名哲学家波普尔、以赛亚·伯林也都认为黑格尔是人类自由的敌人——换言之黑格尔是极权主义的“教父‘之一。从思想的角度,阿伦特的视角显然高于德鲁克的视角。其实苏联和纳粹德国在斯大林格勒大战,无非是为了消灭”异端“,】
附录:黑格尔对后人的影响
来源:维基百科上黑格尔条目
历史学家将受到黑格尔影响的人分为两个敌对阵营,黑格尔右派和左派。黑格尔右派的代表是他在柏林洪堡大学时期的学生们,他们拥护福音正统的宗教观念,拥护后拿破伦时代的政治保守主义。
黑格尔左派,有时也被称为“青年黑格尔派”,他们继承黑格尔学说中的革命成分,在宗教方面主张无神论,在政治领域主张自由民主,其中包括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和年轻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这些年轻的黑格尔信徒经常在柏林希贝尔酒吧聚会、争论,这里的氛围造就了对以后150年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们,形成了无神论、人文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基本观念。
但是几乎没有一位黑格尔左派宣称自己是黑格尔的追随者,有几位还公开批评黑格尔的哲学,但是这种历史上的区分法仍然在现代学院哲学中使用,黑格尔左派对黑格尔的批评导致一个全新的领域—关于黑格尔和黑格尔理论的文学作品。
当代对在校学生来说,为了方便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分为三个阶段,“正题”(例如在法国历史上的大革命)、“反题”(大革命随后的恐怖阶段)和“合题”(自由公民的宪法保障状态)。这种分法并不是黑格尔自己提出的,最早见于费希特的对个人和全体之间联系的一个模拟描述。黑格尔学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三段论法会掩盖黑格尔理论的真实论点,虽然黑格尔曾经说过:“要考虑到两个基本元素:第一,自由的意志是绝对的和最终的目的;第二,实现的方法,也就是说知识和意识的主观方面,包括生命、运动和活动。”(正题和反题),但他没有使用“合题”这个术语,而是用“整体”。“这样我们就了解了整体道德和实现自由的状态,以及其后这两种元素的主观整合。”
黑格尔运用这种辩证法体系解释哲学、科学、艺术、政治和宗教的历史,但是现代评论家指出黑格尔经常修饰历史的真实以适应他的辩证法模式。卡尔·波普尔在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指出,黑格尔体系文饰了威廉三世的统治,他认为1830年代的普鲁士是理想的社会。赫伯特·马尔库塞在他的《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崛起》中批判了黑格尔作为一个国家权力的辩护士,为20世纪极权主义的兴起开辟了道路。实际上黑格尔并没有为这些权力形式辩护,只是认为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因为这些权力存在,所以也是合理的。亚瑟·叔本华藐视黑格尔对历史的解释,认为他的著作是蒙昧主义的,是“伪哲学”,许多英国的哲学家都遵从这种看法。
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是其哲学体系中遭到批判最多的地方。虽不乏可取之处,但不能否认的是他的多处自然哲学论述与自然科学中已发现的事实是相违背的,这或多或少影响了其哲学体系的瓦解。不仅他的哲学体系在科学界名誉扫地,许多科学家对形而上学的厌恶态度也与之相关。德国领袖数学家菲利克斯·克莱因指出,流行一时的新人文主义和黑格尔哲学抑制了柏林的科学生活。直到19世纪20世纪初,通过洪堡(指威廉·冯·洪堡和亚历山大·冯·洪堡两兄弟)的努力,自由的科学生活才开始兴起。
20世纪黑格尔的哲学开始复兴,主要是因为几个原因,一是发现黑格尔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头,还因为黑格尔的历史观开始复活,再有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性得到广泛的认同,将黑格尔的理论重新带到马克思经典中的最重要的著作是乔治·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掀起一股重新了解评价黑格尔的著作热,黑格尔的复兴也引起对黑格尔早期著作的兴趣。现代美国的哲学家也明显受到黑格尔的影响。
附录:左派和右派政治光谱(Left-Right political spectrum)
左翼和右翼之争至少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它们的区分普遍被认为是首先来自于法国大革命时在国民议会中的座位分布,坐在议会主席左侧位置的议员多半持民主的、共和的和激进的立场,他们由此被称为左派;而坐在主席右侧位置的议员多半持君主的、保守的和温和的立场,他们由此被称为右派。就我国情况而言,左右之分的结果很明显,毕竟左衽、旁门左道都是坏的。不过由于左衽对大批理论的吸收和夺舍以及派系分化或缝合,今日的左派、右派划分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挂着同一个词却完全变了味道。比如在美国,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者和新古典自由主义(neo liberalism)者可以成为死敌,在中国捧着马教教义的”皇汉“和手持四书五经的皇汉之间的关系比亚伯拉罕一神教还要势如水火……
附录:王焱《黑格尔左派与右派之战》
今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俄罗斯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庆祝盛典。为世界瞩目的是,德国总理首次应邀出席了这一典礼。这倒让人禁不住想起当年苏德战争炮火正酣时的一段往事。
1941年10月,希特勒挟180万大军、1700辆坦克和1390架飞机,从地上和空中向前苏联发动了闪电战。1942年末,两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展开了一场空前惨烈的殊死大战。有位学者当时却指出,这是黑格尔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战争。战场上的杀戮在此转换成了一个哲学事件。 黑格尔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以其恢弘的气魄,惊人的思辨能力,构建了一个森罗万象的庞大形上学体系。他的哲学从宗教出发,而归宿于政治世界。身处急剧动荡的时代;老黑格尔既亲身经受了法国大革命与启蒙主义的洗礼,又是普鲁士官方的第一哲学家。激进与保守,理性与浪漫,困惑与矛盾,在他的哲学中都有充分的体现。有感于当时德国的萎靡不振,他讴歌强权国家的伟大,向世人宣示“权力的真理”;而放眼“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凯歌行进,他又珍惜个体前所未有的平等与自由。对于政治社会的种种冲突,黑格尔都力图从哲学上加以调和,政治上则依违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他不满康德的二元论,运用“辩证法”的法宝,将一系列两歧性观念加以调和,从而使他的哲学充满了内在的紧张,具备了某种吊诡的特性。
还在黑格尔在世时,即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大学派。大师一旦弃世,众多门生后学各自据其一体,分裂为两个相互对立的营垒。在青年黑格尔左派看来,大师已经将世界解释完了,留给后学的惟余改造世界一事。他们高扬辩证法理论,把黑格尔抽象的观念推演转换为现实的历史演进,实现了从哲学到社会学的大跨越。这一派后来传入并支配了俄国。激进的革命家们“宣布历史——以及其余一切事物——有其铁律与牢固无情的法则。反抗这些铁律,或者抗议它们似乎引起的残酷与不公,是无聊且无益之事”(巴枯宁语)。黑格尔右派则继承了大师保守的方面,沦为德国思想界反动的一翼。他们鼓吹强权国家,宣扬德意志民族独得天命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后来则沦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仆从。
从影响世界之大着眼,一手托两家的黑格尔,可谓达于古今哲学家的巅峰。生前曾有预感的他,曾说:“一个党派只有自身分裂为两派时,才能证实自己是胜利者。”
但要说这些左右后学之间完全对立,也不尽然。他们也分享某些共同的目标、价值与手段。两派都施行计划经济,看好极权体制,都主张警察国家,都追求霸权的无限扩张。前者有大清洗和古拉格;后者则有大屠杀与集中营。有人因此认为,20世纪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两种极权意识形态,皆由黑格尔所发轫。比如哲学家波普就认为:极左派与极右派的政治哲学都“建立在黑格尔的基础上;左派用阶级战争取代黑格尔历史主义框架中的民族战争,右派则用种族战争取代了民族战争。”
伯林则指出,两派对于黑格尔的执迷,盖出自人类对于业已失落了的神秘的整体和“大全”的把握这类“无可救药的形上学欲求”,结果最终导致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残酷战争。检点这场黑格尔哲学内部讨论的后果,苏联为此付出了2000万人死亡的高昂代价,德国则向形而上学的祭坛上奉献了600万人的牺牲。战后,作为西方文明腹心的欧洲,满目疮痍,成了一片瓦砾和废墟。这似乎验证了诗人海涅所说的话,千万不要小看了那些书斋里惨淡经营思想的哲学家们,有一天这些思想从象牙塔中溜将出来,将会把整个世界都卷入浩劫。
作为黑氏后学,两派人马“左右佩剑,各主一偏”,其实都背离了黑格尔以国家法学建构公民身份的政治理想。老黑格尔在弥留之际就抱怨过,他虽然名满天下,却只有一个人理解他的哲学;紧接着又说,其实就连这个人“也没有搞懂”。由此衍生的政治实践的走火入魔,当然不能向哲学家问责。
世界历史才是最终的审判台。古往今来的君王僭主,平地掀翻世界,只手颠倒乾坤,自以为立下不世之功业,可在老黑格尔看来,却统统不过是“绝对精神”用以实现自身目的之工具而已。这就是“理性的狡狯”。一世之雄斯大林,以战场上的胜利赢得了哲学上胜出,可在黑格尔专家科耶夫的眼中,这却意味着世界正在走向“普遍同质化的国家”。觇之于战后60年的历史进程,揆诸俄德两国的政治现状,是耶,非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
西元1969年版序
它当然不是唯一毫无妥协地斥责极权主义教条并坚信纳粹主义才是真正袒护恶魔的作品。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几百部作品都为希特勒开脱。这些书不是假造纳粹主义主义史,将其视为”德国民族性的表现“,就是将其(与法西斯主义)描绘为”资本主义垂死前的挣扎“,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则是即将到来的救世主。然而,本书将”民族性“的说法斥为不经大脑的言论,因为民族性或民族史或许能解释一个民族如何行事,但不能解释他们为何行那些事。本书认为,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蔓延欧洲国家全体的一种疾病。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救世主,相反,我断言,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全盘失败,才是大众逃向极权主义绝望炽焰的主因。
因为书中的结论太过“极端”:,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将会受其内在逻辑驱使,步向“终极方案”,也就是屠杀所有的犹太人,西欧国家的大军将无法有效抵抗德国人,斯大林最终将会同希特勒签署协议。
“异化”(alienation)一词在西元1930年代还不是政治用语,语在《经济人的末日》中也找不到。虽然如此,西方民众与西方社会及以西方政治信条间的疏离异化,确是本书的核心要点。在某些方面,本书提早了十多年指出,存在主义在将于西元1940年代晚期至1950年代初期支配欧洲的政治氛围。书中有两篇重要章节,题为“群众的绝望”与“恶魔再现”,这两个用语今天看来再熟悉不过,但在西元1930年代或说法国国革命之后,都还不算是政治辞令。据我所知,《经济人的末日》也是第一本将克尔恺郭尔(SørenKierkegaard)视为影响现代政治甚深的现代思想家政治的作品。然而,相较于许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探讨存在主义和异化的著述,《经济人的末日》显然是一本社会及政治论著,而非哲学论著(当然更不是一本神学论著)。本书的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地山说道,“这是一有本关政治的书。”的确,本书涵盖了原理、哲学与政治信条,但只是将这些作为具体分析政治动态时所需的材料。它的主题是权力的崛起而非宗教信仰的兴起。《经济人的末日》不太探讨人性,甚至对于社会本质也很少提及。它专注于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欧洲社会及政治结构的瓦解导致纳粹主义的兴起,进而支配了整个欧洲。构成本书主线的是政治、社会与经济,而非精神上的苦痛。
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著作,《经济人的末日》将欧洲的这一悲剧解释为丧失政治信念的结果,也是欧洲民众政治疏离异化的结果。本书特别追溯了人们一头栽进极权主义绝望的过程,并将之归咎于进入“现代”的三百年来,人们对政治信条的不断幻灭。最后一个出现的信条是马克思主义。而导致极权主义兴起的决定性因素,正是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全盘失败,面对政治现实和社会经验,它显得苍白而缺乏说服力。结果是,欧洲的民众被“再现的恶魔”所征服。“现代”的核心信念,是社会可以被建立成理性的、有序的、可控的并且可理解的。随着马克思主义作为世俗信条的崩解,欧洲社会再度变得非理性、险恶且令人无法理解,不断遭受邪恶力量的威胁,个人毫无抵御能力。失业和战争是两次世界大战间困扰社会的“恶魔”。自由主义欧洲的世俗信条(马克思主义正是其合乎逻辑的最终形式和顶点),无法驱逐也无法控制这些力量,既有的经济与政治理论也无法解释其成因。虽然其源自人类和社会,并于社会内部发生。但结果证明它们竟和那些曾令人类先辈无能为力而不得不屈服的恶劣的自然力量一样,没有理性、无法掌控、毫无意义而又变化无常。
【注:德鲁克认为自由主义欧洲的世俗信条的最终形式和顶点,确实很有洞见性,毕竟一战才出现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现在是欧美的统治思想。】
《经济人的末日》对于宗教的尊重,以及对于基督教教会的重视,在当时可能有点过时。
【注:德鲁克看不出极权主义和基督教的关系,显然眼光有限。不过亚伯拉罕一神教版本越古老,对人类文明的危害性越小,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呼吁也不无道理。】
在那个年代,“革命”的呼声沸沸扬扬,但这个词的内涵,却像是抢椅子的游戏,由马克思主义的“无阶级产专政”取代“资本家老板们”。本书可以说是第一次解释了这种所谓的革命,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是新的统治者不得不暂停现有的权力架构和机制而已。这在今天是老生常谈,因为我们有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米洛万·吉拉斯的《新阶级》和西元1968年秋天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在三十年前,这是一种崭新的观点,连当时的“反共产主义者”也确信,共产主义将彻底改造社会,而不是以一个更为严苛和集权的统治集团来代替原有的。
【注:德鲁克既然也认为共产主义将彻底改造社会,而不是以统一个更为严苛和集权的统治集团来代替原有的,哪为什么还认为这种所谓的革命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当然这也可能是翻译人员的错,儿子要维护爹地也是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措辞上也有很大问题,比如集权是动宾短语,和严苛这样的形容词显然是不能并列的,极权才是常用的有关形容词。这块存疑,但暂时找不到原文,姑且说这么多。】
我发现,当时所谓的“革命”,绝大部分不过是权力斗争而已。我认为,有关生产和分配体系的某种特别的社会及经济体制(即资本主义),不但会继续存在,还极可能在未来证明其有带动经济发展的能力。而马克思主义由于其美满的特质,一旦这种绝对正确遭到质疑,大概就难以幸存。三十年前我提出这个观点时,大家都认为,传统经济一定熬不过战争摧毁的这个结论再“明显”不过了。但后来的发展却大大出乎意料之外:欧洲经济复苏,欣欣向荣,以民营企业和私人国际企业为基础的世界经体系济日益茁壮。
但当是我体认到那些同时代人眼中“无法避免的革命”不可能发生的时候,我也发现新的极权主义,尤其是德国的纳粹主义,才是真正的革命:其目的于在推翻某些比经济体制还基本的东西,比如价值观、宗教信仰和基本的道德观。这场革命将希望化为绝望,以魔幻代替理性,而人们的宗教信仰将会化成恐惧、疯狂、嗜血的暴力。
【注:德鲁克既然认为有新的极权主义,为什么不聊聊的旧的极权主义呢?】
本书亦描绘了当时的第二个特点,这在今天同样难以想象:马克思主义是当时多如繁星的社会政治运动、哲思与激情中的超级巨星。本书宣告(也试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已在欧洲失败,也不会与发达工业国家产生任何瓜葛。引用一本比《经济人的末日》晚了二十年的书名,当年的马克思主义可比喻为“失败的神”。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属于马克思主义那段富有创造力的时代已经画下句点。大战前数十年间,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欧洲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中,许多创造性思想的源泉。甚至连当时的反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定义自己。大战前数十年的欧洲,可以说根本没有非马死思主义者存在。但后来,社会主义国际(又称第二国际)并不能避免、平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西元1918年大战结束后,尽管欧洲大陆无论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都徒留一片衰败与混乱,共产主义也无法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执政掌权。从此,马克思主义很快在欧洲丧失了活力,成为聊具仪式的咏叹。
西元1914年前被马克思主义迷住的精英们,在西元1918年后,几乎全盘抛弃,转向新的政治领袖和新的思想。德国马克斯·韦伯,法国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和奥地利的弗洛伊德(仅列出知识分子中最耀眼的人物)都不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大体而言,他们并不觉得马克思跟他们思考的问题有什么关系。而马克思主义虽然在一战前造就了一大批思想家和政治领袖,但在一战过后,却没有培育出一个一流的人物,甚至连二流的都没有。
不过,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精英眼中迅速丧失可信度和创造性的同时,却变得通俗和流行起来。什么词汇都可以套上马克思主义,就像西元1950年中代期精神分析突然在美国流行起来一样。马克思主义不再是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兜里的金条,而成了“中等教育程度者”手中的零钱。无论藉由选举或革命,马克思主义都无法再有效地组织以获得权力或拥护者。然而,野心家却可以肆无忌惮地操弄马克思主义辞藻,就像黑索尼里那样,用支离破碎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拼凑出“反马克思主义”,以掩饰他们智识上的贫乏。这种情形甚至在美国也出现过。在马克思主义富有创造力的年代,它对美国没有影响,没有哪一位美国一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但是在西元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初,在欧洲逐渐衰退的马克思主义却为美国的伪知识分子们提供了一套说辞,作为他们思考和分析的代用品,长达十年之久。
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这个“失败的神“在衰败之后对于欧洲政治舞台的影响力,反而大于其之前作为世俗宗教的颠覆时期。《经济人的末日》中讲得很清楚:,造成极权主义兴起,导致大众逃向极权主义绝望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失败,而并非其胁迫与承诺。
【注:德鲁克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俗宗教,也算有点眼光,也介绍了一点关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不过这几段话可以吐槽的内容太多了,马克思主义怎么不能无法再有效地组织以获得权力或拥护者了?中国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和柬埔寨的大屠杀等证明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度仍旧极高。至于德鲁克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极权主义的一种,显然也是有问题的。】
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很难理解,要不是丘吉尔,美国可能将听由纳粹势力主宰欧洲以及几乎所有的欧洲殖民帝国。事实上,要不是丘吉尔提早一年让纳粹破功,说不定连苏联也无法抵挡纳粹的侵略。丘吉尔页献的正是欧洲迫切所需要的:道德的权威,对价值观的信仰,对理性行为正当性的信仰。
【注:德鲁克本质还是爱马爱苏的,显然丘吉尔只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失败者。抛弃丘吉尔对中国的各种打压不论,丘吉尔一心要维系的大英帝国因为和德国提前开战被打崩了,战后又被美苏联合肢解了,不知道尬吹丘吉尔的人是什么货色。道德这个词被morality严重污染,这个以后再论。】
但在我们眼中,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并不在其中。
【注:从这里可以看出德鲁克的前后矛盾——这里又认为斯大林体制也是极权体制。】
尽管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与二三十年代不同,现实环境也有差异,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某些反应,不禁使人联想到曾将欧洲推向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推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群众的绝望”。一些团体的行为(种族主义者,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或者是所谓左派学生的行动主义者),不禁让人毛骨悚然地联想到和希特勒麾下的冲锋队队员。他们否认他人拥有任何权利,比如言论自由;他们诽谤他人的名誉,更以蓄意破坏为荣。他们的辞令像极了希特勒,像到令人厌恶。他们那些满脑仇恨的先知所保持的虚无主义,跟希特勒没什么两样。他们的直系先辈正是西元1910年代至1930年代德国的“青年运动“一一留长发、弹吉他、唱民谣。我们也许还记得,德国的青年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是打着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旗号的,最后却成为了希特勒最狂热的中坚信徒。
【注:过去的日本赤军、美国的嬉皮士等以及今日之毛粉、小粉红、自干五也是上述成员的一部分。扩大了11万倍的“反右运动”所揭示了一条重要原则——只要足够左,看谁都是右派!情况不对,就开除别人的左籍是左衽的基本技能。苏联也这样开除了纳粹党的左籍,大陆的小粉红也开除了紧紧跟随苏联的印度斯坦的社会主义籍……
纳粹党只是个简称,全程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德语: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 Partei,缩写为NSDAP),简称国社党,通称纳粹党(英语:Nazi Party),纳粹来自德文中的Nazi,为“国家社会主义”(德语:Nationalersozialismus)的简写。由于残存的左派把希特勒开出了左籍,纳粹党常被视为极右翼政党。但如果纳粹党是极右翼政党,那么要复辟霍亨佐伦王朝的容克贵族算是左派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也是常常搞混的,不过纳粹党显然不是民族主义政党,不然也不会送大批德国人去死。苏联和纳粹德国的战争是一神教战争的一部分,不过这种战争是处于高级阶段,看着不似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战争而已。】
附录:知乎用户风龙云虎评价丘吉尔
# 如何评价丘吉尔?作为首相,作为他个人,他一生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自大狂,南辕北辙的疾跑者,极度缺乏战略眼光的决策者。对个人来说,他追求的权力、名望、金钱都实现了,但从政治抱负讲,他一心要维系大英帝国的目标则被其一手葬送,最终大英帝国在他推波助澜的战争中被摧毁,廉价转卖给了美国。丘吉尔所为,都让我怀疑从其美国母亲嫁到英国就是美帝在下一盘潜伏并安置定时炸蛋的大棋。
简单的说,二战前以英国的国力,是绝对无法撑过一场全欧乃至世界大战的。无论胜负,英国被卷进世界大战必然会导致其殖民帝国的崩溃。如果一战前这还被视为异想天开,而到二战前如果还认识不到这一点,只能说毫无自知之明,缺乏基本战略眼光。所以要么在希特勒羽毛未丰前就先下手为强,如果延误了窗口期,当德三已经成为欧陆军事强国后,最佳选择就只有与德国合作,将其攻击方向转移到苏俄,这才是最理性的选择。
所以为什么希特勒一直认为攻击波兰不会引发与英法的战争,为什么苏俄一直攻击西方“祸水东引”,甚至战后也一直如此宣传?因为从正常理性战略角度,英法“祸水东引”是最有利最明智的选择。即便英法以打败德国为目标,也该等德俄两败俱伤之机再插手才符合逻辑。结果是英法居然给神经不正常的波兰开空头支票,并主动对德宣战,一面引爆全欧乃至世界大战,一面将德国主要攻击力引到自己头上,搞“祸水西引”,这是稍有战略头脑的人无法理解的。
附录:文化马克思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和同盟国的工人等无产阶级打得不亦乐乎,一点不讲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情。战争后期列宁领了德国马克回到俄国建立苏联,也不见德国工人支持苏联。此外共产主义的理想先在较为落后的俄国落地生根而非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的那样——共产主义理想先在欧美发达国家实现。这些都说明马教原始教义出现了致命的bug,于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都是文化惹的祸,必须对原有文化进行解构和改造。
在阴谋论的用法之外,“文化马克思主义”一词偶尔也被学者用来指代有关精英群体如何利用文化生产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学术研究领域。但一般没有人会自称“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有时这个词也被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发明的“批判理论”一词的同义词。“批判理论”一词最初就是用作马克思主义的委婉词。更一般地说,俄罗斯以外,将马克思主义思想重点从经济学转到文化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被称作“文化马克思主义”。
西元1922-1923年间,包括费利克斯·威尔、卡尔·科尔施和卢卡奇·格奥尔格在内的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法兰克福成立了社会研究中心。他们主要研究的主题是为何西元1918年的11月革命会以失败告终,在经济方面他们使用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但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他们使用了其他的思路,比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一些理论。西元1929年前后,麦克斯·霍克海默正式开创了法兰克福学派,除了社会研究中心的一批学者外,外界的一些学者也加入了法兰克福学派。之后几年里,霍克海默意识到了纳粹主义的危险,并于西元1935年将研究所迁到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此后,法兰克福学派着力于研究极权主义,以免像纳粹这样的极权国家卷土重来。麦克斯·霍克海默和狄奥多·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及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中皆从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角度分析了文化工业。他们担忧大众媒体会向民众灌输虚假意识,阿多诺就这一点提出了威权人格一词,用来解释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人民依然容易卷入法西斯运动中。
二战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回到了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转移到了以于尔根·哈贝马斯等人为首的第二代学者身上。马尔库塞则留在了美国,成为了与新左翼有关的争议性人物。马尔库塞有关压抑性容忍的论述,以及他对安吉拉·戴维斯和鲁迪·杜契克等学生的指导使得他在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和德国六八学运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与马尔库塞相反,大多数法兰克福学派人士尽量避免参与新左翼的活动,例如哈贝马斯就建议学者们采用“冬眠政策”。随着西元20世纪70年代新左翼的衰落,法兰克福学派曾采用的批判性教学逐渐主导了美国高等教育界,这套理论也招致了20年后有关政治正确的一系列争论。
阴谋论者声称一小批马克思主义精英分子和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正在颠覆西方社会。这种指控显然有明显的证据,即他们引述的一部分理论确实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使用。
米歇尔·明尼希诺于西元1992年出版的《新黑暗时代﹕法兰克福学派和“政治正确”》一书。他在书中宣称基督教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理念已经被“丑陋暴政”的现代艺术所取代,并将此归咎于一个所谓在美国灌输文化悲观主义的阴谋,由卢卡奇·格奥尔格、法兰克福学派和媒体精英人物分三阶段进行。 明尼希诺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有两条毁灭西方文化的途径。其一,是狄奥多·阿多诺和瓦尔特·本雅明的文化批判理论,通过艺术和文化传播马克思的异化论,并用社会主义取代基督教:具体而言,是通过舆论调查及宣传洗脑控制大众;其二,是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埃里希·弗罗姆颠覆父权的女权、性解放、多形变态运动。明尼希诺还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应该为西元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及“迷幻药物革命”负责,因为他们通过分发迷幻药物以提倡性变态和淫乱。
被越南共产党纠缠的美军又被受苏联暗中支持的嬉皮士”反战活动“影响被迫从南越撤离,这标志着两大马克思主义流派联合体对阵美帝国主义的巨大胜利。南越的覆灭不仅代表中国少了一个重要盟友,也导致了数十万华人被抄家驱逐或是沦为怒海中的一具尸体……
西元2011年7月22日,挪威极右翼恐怖分子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西元2011年挪威爆炸和枪击事件中杀死了77人。事件发生前约90分钟,布雷维克向1003人发送了包含他1500页政治宣言《2083:欧洲独立宣言》和一份《政治正确:一种意识形态的简史》拷贝的电子邮件。他在政治宣言中主要讨论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并声称“西欧性传染病流行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文化马克思主义将穆斯林、女性主义女性、同性恋以及少数群体视为‘美德’,将欧洲的基督教男性视为‘邪恶’”、“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被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控制”。
除布雷维克外,还有一些其他极右翼恐怖分子同样相信文化马克思主义阴谋论。曾计划谋杀工党议员罗西·库珀的英国新纳粹、虐童癖杰克·伦肖在为英国国家党制作的视频中表示相信文化马克思主义阴谋论。西元2019年加州犹太教堂枪击案的策划者约翰·T·欧内斯特自称受到白人民族主义启发。在一份在线文档中,欧内斯特表示“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传播是犹太人在背后推波助澜”,因此“每个犹太人都要为精心策划的欧洲人种种族灭绝负责”。
我国百年来深受两种马克思主义的荼毒,面临的情况比欧美差得多。不过由于稳定压倒一切,岁月静好成为主流思潮。只要昊天上帝还没有抛弃我们漢人,那么中华文明就还有复兴的希望!
前言
同时,本书依据于一个先入为主的信念:欧洲传统与极权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间,毫无妥协余地。
【注:可笑,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固然互相敌视,但这也不妨碍它们都信奉亚威,都尊耶稣。人不能太傻,祂们换了个皮肤就不认得了?
在本书中,我试图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诠释成一种根本性的革命,并有意将此分析局限于社会和经济领域,虽然我不相信唯物史观。我认为物质绝对不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只不过是人类存在的支柱之一。从人类具有双重本质、同时隶属于兽性与神性领域现象的来看,物质绝不比另一条支柱一一精神支柱一一来得重要,虽也毫不逊色。
【注:这种思想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想。】
其次,前几个世纪的特性是,人类致力让精神层面为物质层面服务。好比要分析西元16世纪的宗教改革在社会和经济层面的起源,显然是最迂回且浪费时间的方式,因为从西元13世纪到16世纪的特征是,人类一直试图让物质附属于精神领域之下。
【注:如果这种说法符合事实,那么马教宣称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这种说法有了个明确的新教起源。】
第一章 反法西斯主義的錯覺 The Anti-Fascist Illusion
短短几年内,法西斯极权主义已经成为全球革命的主要潮流。它变成欧洲唯一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让民主制度无力抵御内忧外患。全球各种分歧甚至矛盾的运动,都拿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及措辞当幌子:近东地区的民族新主义、远东的旧封建主义、拉丁美洲传统的军事政变和“种族觉醒”、亚非殖民帝国的宗教反抗,皆自称为“极权主义”;三十年前的民主政体运动和十年前的共产主义运动,着实也该打这面旗帜才是。而共产主义这场昨日的世界革命,不止被迫认承仅能自卫,也不得不承认丧失了战斗力。不论共产主义领袖的脑中对遥远的未来还有什么高见,他们和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民主组成联合阵线、对抗法西斯主义的结果,是再也当不成革命力量,也等于宣告放弃了要做未来社会秩序之先驱的承诺。“法国人民阵线”的无能以及发生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后,联合阵线思维的彻底溃败,都表示共产主义再也无法有效抵抗法西斯主义。
上文完全是展示如何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至少我们中国没人自称极权主义。当然也可能是翻译的问题。
从极权主义在国外普遍遭遇敌意的情形来看,它能如此迅速取得优势,实在惊人。世人无不害怕极权主义的残忍、担忧它的激进、憎恶它充满仇恨的口号及信条。与之前所有革命不同的是,即便是旧秩序国家的少数族群,也无法接受极权主义的宗旨、精神和目标。然而,法西斯主义仍稳定地取得进展,直到称霸欧洲。
世人无不害怕?上文还在说全球各种分歧甚至矛盾的运动都自称极权主义,这里就说世人无不害怕,呵呵,胡说八道也得有个度吧?当时美国、中国、英国等都有一大批希特勒的支持者,直到现在希特勒及其代表的精神仍在支撑有良知的人们抵御白左、红左势力,如让白左物理绝户的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在法庭上频繁行纳粹礼;参与拍摄希特勒相关电视剧《Look Who's Back》的演员Oliver Masucci扮成希特勒的样子在柏林街头行走,受到了围观与追捧,还有人恳求他:“请把集中营带回德国吧!”。今日欧洲没白左搞成现在这鸟样,导致右翼势力重回视野。这充分证明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毕竟法西斯主义本身的目的是要消灭要消灭人类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势力。
为何那些坚定的民主派反对人士,制止不了这个危及他们所有信念的最大威胁呢?原因并不是怯懦。为了对抗法西斯,西班牙有无数人捐躯,奥地利工人牺牲性命,意大利和德国也有许多默默支持反对运动的无名劳工,这些人的英雄气概无庸置疑。但是,若勇气挡得住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早就被阻止了。
德鲁克既然能认同乔治·奥威尔的《1984》为什么不反对差点把奥威尔当托派宰了的西班牙共产党?前后逻辑矛盾很明显啊。佛朗哥作为西班牙传统秩序的捍卫者,保卫罗马公教会,杀了一点打砸教堂、杀修士、奸淫修女的西班牙共产党员,但自诩提倡宗教价值的德鲁克为何对此视而不见呢?反而一味的吹捧共产主义者抵御法西斯主义者,可笑!
西班牙内战起因当然是共产党员迫害右派人士特别是教会成员,导致民众起义推翻”共和政府“,愿意向政府投诚的佛朗哥也被迫站在前台,把”政府“成员送进坟墓。共和军在内战中约将55,000名国民军派人士处决,其中最有争议的是共和派民众攻击罗马教会,神职人员约有7000人被杀害。在国民军起先发动起义时,共和派民众逮捕许多国民军将领和右翼保守派民众,将其杀害、狱中服刑的囚犯也在受到虐待后被处决。马德里约有11705人因此而死。共产党员圣地亚哥·卡里略与部属执行了帕拉库埃略斯和阿尔多斯附近的屠杀,数千人罹难(包括妇人与孩童),是战争期间最大规模的屠杀行动,但是由谁负责此行动也有争议。另外,共和军也有对共产党员的处决行动,安德烈·马蒂(André Marty)杀害了5000多名国际纵队的士兵。共产党内的斯大林主义者也杀害了国际纵队内部的部分人士,如亲托洛茨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相关人士,包括领袖安德烈斯·宁。约有6832名神父、修女和僧侣遭到共和派军民杀害,其中有13名主教、4172名教区司铎(diocesan priest)、2364名修士和283名修女被杀害 。
第五纵队不等于国际纵队,这倒是第一次了解。
西元1936年至1939年间,西班牙内战时期,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领导起义军与西班牙人民阵线军发生冲突,佛朗哥手下一名将领埃米利奥·莫拉派遣四个纵队(columnas)进攻首都马德里,当记者问起他的作战策略,他说他已调派四个纵队包围著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另指挥著一支纵队潜伏在马德里城里做内应,实际上这只是为了敷衍记者的回答,然而共和政府认为关在监狱中的政治犯们就是莫拉口中的第五纵队,因而连夜将一千多名政治犯处决。
国际纵队(西班牙语:Brigada Internacional、英语:International Brigades)是由共产国际组建,在西班牙内战中援助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尤其是其中的人民阵线)的军事单位。国际纵队受第三国际的强烈支持,代表苏联对西班牙共和国所承诺的援助(包括武器、补给、军事顾问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应法西斯意大利、法西斯葡萄牙和纳粹德国对国民军的援助。国际纵队的多数成员是法国共产党的成员或是意大利和德国的流亡共产党。也有许多犹太人参与了国际纵队,其中以美国、波兰、法国、英格兰和阿根廷志愿者中的犹太人居多。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人一般不会加入国际纵队,而是会选择人民阵线中一些较小的党的民兵加入。例如,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由托洛茨基主义、右翼反对派及其他反斯大林主义左翼共和党人组成,并且不对西班牙人和国外志愿者(比如乔治·奥威尔)做出明确的区分。也有共和党人选择加入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例如杜鲁蒂民兵单位、国际工人协会及全国劳工联盟。纵队成员还包括一批诗人、艺术家、医生和记者,如加缪、聂鲁达、海明威、奥威尔、毕加索等。甚至还有不少”华人“参与如谢唯进担任国际纵队炮兵纵队政治委员。
西元1936年底,奥威尔写完他那本关于英格兰北部威冈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通往威冈码头之路》后,抱着“这种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制止它”的心态前往西班牙。由于他抨击过许多英国著名的左派,受到共产党的猜忌。他转而通过一个小党(独立工党)前往巴塞罗那──而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外国志愿者那样加入由共产党组织的马德里国际纵队──并被介绍给其盟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简称统一工党)。统一工党的领袖Andres Nin本人曾经参加过托洛茨基领导的国际左派反对派,后来与反对派分裂,另与人组织统一工党。该党被斯大林派指为托派,但事实并非如此。西元1937年6月,共产党对统一工党和无政府主义工人、民兵施行大清洗和大屠杀。奥威尔侥幸从西班牙逃出。据后来披露的莫斯科党中央档案,奥威尔本人也在苏共的黑名单之列。详细内容可参照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 第五章:
表面看来,共产党和统一工党之间的不和是战略上的不一致。统一工党是为了当前的革命,而共产党不是。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而双方还有很多分歧。不仅如此,共产党坚持认为统一工党的宣传分裂并了政府势力,因此会危及到战争,其次,尽管我最终不这么认为,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能证明我这种想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在这一点上共产党独特的策略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最初有点犹豫不决,提着就开始断然地宣称统一工党正在分裂政府势力,不是由于判断失误而是有意谋划的。据称统一工党只不过是一群伪装的法西斯分子,受雇于佛朗哥和希特勒,他们在强行贯彻一项伪革命政策来支持法西斯事业。统一工党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的组织和“佛朗哥的第五纵队”。这个组织包括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其中包括八千或一万正在前线战壕里挨冻的士兵,还有成百上千来到西班牙与法西斯作战的外国人,这些人这样做常常是牺牲了自己的生计和国籍,但只不过是受雇于敌人的叛徒。这种说法通过招贴画等手段在西班牙流传开来,而且被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和亲共产党的新闻界不断重复。如果我愿意收集的话这些引语够我写六本书。
当时他们就是这样宣传我们外国人的:我们是托洛茨基分子、法西斯分子,叛徒、杀人犯、胆小鬼、间谍等待。我承认这些话很不中听,尤其当你想到那些该为此事负责的人。看到一个十五岁的西班牙男孩被人用担架从前线抬下来,从毯子里露出一张茫然的惨白的脸,再想一想伦敦和巴黎的那些健壮的人却在撰写小册子来证明这个男孩是个伪装的法西斯分子,这真令人痛心。战争最可怕的特征之一就是所有有关战争的宣传,所有叫嚷、谎言和仇恨都无一例外地来自那些没有参加战斗的人。我在前线认识的统一工党民兵,我常常遇到的来自国际纵队的共产党员就从来没称我是托派分子或叛徒;他们把这些都留给了后方的记者们。那些撰写小册子来反对我们和在报纸上中伤我们的人都呆在家里安然无恙,或最坏也是在巴伦西亚的报社办公室里,这里离子弹和污泥有几百里的路。除了诽谤党内斗争,战争通常有的垃圾,大肆宣扬英雄事迹,敌人的中伤——像往常一样所有这些都是由那些不打仗的人来完成,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会在战争一开始就避开一百公里。这场战争最令人生厌的结果使我认识到左翼与右翼新闻界完全一样骗人和虚伪。
所有抵抗法西斯威胁的运动皆徒劳无功的原因,在于我们根本不知道在抵抗什么。我们知道法西斯主义的表征,却不了解它的起因及意义。而那些自称反法西斯主义者、将反对法西斯作为主要信条的人士,所坚决抵抗的是他们自己捏造的幻觉。这种无知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民主国家的部分人士一厢情愿地认为,法西斯式的“激进主义”只是过渡,以及反法西斯主义者认为法西斯主义“不会长久”的错觉,都是民主无能抵御法西斯的原因。因此,分析法西斯主义之成因,看来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 除了某些明显曲解证据、根本不必特别反驳的主张外(如法西斯国家多数民众私下皆对政权怀有敌意,只是遭到恐怖政治镇压),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一般有三种说法:一、它是人类原始残忍野性的恶意爆发;二、它是资本主义一时的成就,目的是为了拖延或防止社会主义终将得到胜利;三、它是无耻而技巧完美的宣传手法,对愚昧大众及其本能之影响的结晶。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早就强调过法西斯主义是对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击,就如长枪党起义是为了反抗人民阵线的暴政。德鲁克显然对当时的情况没什么了解,只知道一味地反法西斯,却不知道法西斯为何会出现,哎!
至于把法西斯主义视为资本主义拖延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一搏,纯属谬误。说“大企业”(big business)助长了法西斯主义并不准确;相反,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支持者和赞助人在工业及金融阶级所占的比例非常之小。说“大企业”从法西斯主义那里获益也同样不准确,它还可能是所有阶级中,受到极权主义经济和国防经济(Wehrwirtschaft)创伤最重的一个。更荒谬的是,竟有人坚持,资产阶级(甚至其他任何人)有理由担心劳工阶级在法西斯上台前的意大利和德国获得的胜利。这整套理论只不过想扭曲历史,是站不住脚的辩解,不是认真的说明。
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显然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这种说法的荒谬性也就不证自明了。德鲁克的这套理论除了贡献了极权主义这个词之外,也只不过想扭曲历史,是站不住脚的辩解,不是认真的说明。
然而,法西斯主义否定过去的程度,远远超过之前任何政治活动,因为它把这种否定当作最主要的政纲。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否定了本质对立的思维或趋势。法西斯主义反对自由,但反对也保守;反宗教,也反无神论;反资本主义,也反社会主义;反战争,也反和平;反大企业,也反对被认为是多余的技工与店主——这份清单可以无限延伸。纳粹也是典型的例子,它所有宣传的主旨不是北欧人种,不是纳粹主义的承诺、征服或成就,而是反犹太主义——攻击希特勒执政前的“十四年”、攻击外来的阴谋。多年前,我曾听到纳粹煽动者在一场农民疯狂欢呼的集会中宣称:“我们不要面包太便宜,我们不要面包太贵,我们不要面包的价格一成不变——我们要只属于国家社会主义的面包价格。”这是我听过最贴近法西斯主义的诠释。
亚伯拉罕一神教的现代版本远超之前的一神教版本有什么问题吗?自由和保守是本质对立的思维或趋势吗?……另一个现代版本用唯物辩证法整合对立统一规律成功让人拥有了双重思维(Double Think)——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War is Peace,Freedom is Slavery,Ignorance is Strength.),显然技高一筹。
至于那个面包价格问题,我觉得有点搞笑,只要在原来价格上下浮动一分钱不就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了吗?这有什么难的??既然人们要国家社会主义的面包价格,为什么还是反社会主义的呢?
在这些对欧洲传统的否定中,有一项格外重要:驳斥“政治与社会秩序及依其建立的当权机构,必须证明自己在造福臣民”的需要。在法西斯主义眼中,几乎没有哪个过去的概念或思维,比权力的正当性更为荒谬。它认为“权力本身就是它的正当性”是不证自明的。从这句新格言在欧洲广为接受且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程度,就可看出极权革命已深得人心。事实上,这是最惊人的创新。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两千年,权力与当权者的正当性,一向是欧洲政治思潮与欧洲政治史的核心问题。而在欧洲人信奉基督教后,所谓权力的正当性无非就是藉由行使权力为臣民谋福利——拯救他们的灵魂、创造“更好的生活“,或者让最多数人达到最好的生活水平。连拥护完全君主专制的最狂热分子都不敢另作他想。西元16世纪提出君权神授概念的德国新教神职人员,以及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和法国作家波舒哀,皆为证实臣民的利益而煞费苦心。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弗利之所以受尽同时代的人及后世的蔑视,完全是因为他对权力之道德正当性漠不关心,这态度害这位诚恳老实的男人在道德上遭到排斥——即使身在腐败而权欲熏心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所有立基于欧洲传统社会的制度,权力当正性一定是核心问题。因为就是单单透过这个概念,才能将自由与平等(或如之前所说的:正义)投射到社会与政治的现实状况中,而基督教传入欧洲以来,自由与平等就一直是欧洲基本的精神思想了。但对法西斯主义来说,这个问题除了像是可笑的“犹太自由主义”残骸外,根本不存在。
德鲁克可算是掌握了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精髓。槽点太多,我都懒得反驳了。欧洲人才阔了三四百年就瞎吹一地,但国内一堆洋奴膝盖骨都跪没了,只能狂舔洋人的臭脚,沐浴一下”自由平等“的光辉,也不知道他们看到开头是否还想着消灭造福臣民的明君清官侠士追求吗?毕竟洋大人不仅热爱明君、清官,也热爱RobinHood这样的绿林侠士。中世纪的欧洲人有宗教信仰自由吗?有言论自由吗?有迁徙自由吗??贵族和平民平等吗???直到明末,耶稣会才给欧洲人带过去文明的模板,”中国热“让欧洲人有所凭据来反对基督教的反人类统治,典型的如崇拜孔子的伏尔泰、魁奈等人,之后”自由平等“这种口号才成为政治理论的一部分。虽然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不是什么好东西(参见James Stephen《自由平等博爱》一书),但这显然是被左衽夺舍的结果。
英国政府因为是由成熟男人组成,故向命运要求更不可能发生的奇迹:它希望德国发生革命、经济危机或苏德战争爆发。两者都希望能有违反一切事理的奇迹出现,因为另一种选择实在恐怖得难以面对。两者都因为绝望而祷求奇迹出现,群众转向法西斯求助的原因也是此如。
德鲁克居然认为苏德战争爆发是违反一切事理的奇迹出现,其眼光确实很独特!这么说来,当时英国决策层还不是那么脑残,虽然后来是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自大狂丘吉尔上台。
群众的绝望,就是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关键。不是“暴民造反“,也不是”无耻宣传的胜利”,而是旧秩序瓦解又缺乏新秩序所造成的彻底的绝望。
这也算是一种合理解释——面对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进攻,人们在绝望下选择了法西斯主义。
附录:人民阵线和民主阵线(国民联盟)简介
人民阵线是西元193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由不同性质的政治团体组成的广泛联盟,通常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有时还包括自由派、中间派。西元1933年2月,德国纳粹党上台执政。共产国际即提出“法西斯就意味着战争”。1934年国会纵火案嫌犯季米特洛夫当选共产国际总书记。1934年共产国际即提出了人民阵线,代替了极左的“第三时期”理论。该理论把处决工运领袖的社民党称作“社会法西斯”。 1934年5月《真理报》发表文章,提出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作。1934年6月,中左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莱昂·布鲁姆1934年6月与法国共产党、1934年10月与中右的激进党签署合作协议。1935年5月签署《苏法互助条约》。1935年7月20日召开共产国际七大,决定政策彻底转向,在各国推动“反法西斯反战人民阵线”,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团结起来,遏制法西斯国家发动世界大战。随后,人民阵线在法国、西班牙、中国取得了成功。1936年5月,法国人民阵线赢得大选(378席对220席),莱昂·布鲁姆组建政府。英国国民政府虽然是左中右大联合政府,但政治上不够成功。在意大利,意大利社会党拒绝与意大利共产党结盟共同反对法西斯。在美国,美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提出“跟着罗斯福走,一切服从罗斯福”的口号,表现极为民粹主义,被称为“白劳德主义”。共产国际七大后,“人民”作为政治概念开始被各国共产党广泛使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指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这是《毛选》中首次使用“人民”一词。这以后,中共开始大量使用“人民”这一概念。随后的红军出陕北东征战役中,1936年3月1日,彭德怀与毛泽东以总司令、总政治委员名义签发《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不再使用中国工农红军名称。
连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种恐怖组织也是人民阵线的一部分,可见其本质。人民阵线和民族阵线不只是不同,还势如水火。(后者经常被翻译成国民阵线)。
國民聯盟(法語:Rassemblement national,縮寫為RN),西元2018年6月前稱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是法國的一個極右民粹主義政黨,由冉-馬里·勒朋在西元1972年成立。民族陣線在其網站表列各項政綱,主張:
- 回歸傳統社會價值:讓墮胎更為困難或非法化;給予無業母親補助金;促進傳統文化,反對多元文化主義及同性婚姻。
- 脫離歐盟和其他國際組織。
- 徵收關稅或建構其他保護手段對抗廉價進口。
- 加強各種罪刑的刑罰,並主張通過公投恢復「最嚴重罪行」,即死刑。
- 禁止非歐洲國家的移民及難民進入。
- 該黨反對非歐洲國家的移民,特別是來自北非、西非、中東的穆斯林國家。
在西元1995年法國總統選舉發送給選民的小冊子中,冉-馬里·勒朋提出用「人道、尊嚴的手段」將「三百萬非歐洲人」「送出」法國。西元2002年法國總統選舉,更為強調秩序與法律議題。民族陣線的主題包括加強執法、刑罰與恢復死刑。民族陣線經常反抗他們所認為的「權勢集團」,包括其他法國政黨與多數記者。勒朋將主流的政黨(法國共產黨、法國社會黨、法國民主聯盟、保衛共和聯盟)稱為四人幫。民族陣線經常自稱「受害者」或「局外人」。
第二章 群眾的絕望 The Despair of The Masses
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正是欧洲宗教与社会秩序崩溃的结果。造成这些秩序崩溃最终也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欧洲群众对马克思社会主义信仰的彻底崩解;因为事实证明它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建立新秩序。 …… 承诺要战胜资本主义下不平等、不自由的社会,再透过无阶级社会实现自由和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原因。也导致了它的没落。正因为历史证明,它不但无法创造无阶级社会,甚至可能促成更僵化、更不自由的阶级模式,因此马克思社会主义已不再是一种信条。从作为未来秩序的福音、承诺以革命客服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马克思社会主义后来已经变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如此一来它才会更具影响力。但是,一个竭尽心力搞反对的运动,其诉求和根据必定源自它要反对的系统。当社会主义的功能只剩下批判,若还要在社会发挥影响力,就必须依赖资本主义的存在和根据。社会主义虽然可以削弱资本主义的信念,却无法取而代之。一旦资本主义崩溃,马克思社会主义也就丧失所有根据和正当性了。
马克思社会主义后来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对的立面?本来就是对立面,好吧?
由于实施社会主义必然产生这样的社会,因而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基础完全无效,无法成为未来秩序的先驱。
这样的社会指一个等级更加森严的社会,特供一直都存在,没必要多说。
在前资本主义和前工业化的殖民或封建国家,如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西班牙、亚洲殖民地及拉丁美洲等地,马克思社会主义仍是信仰所系。这些地区的社会状况使无阶级社会看来可行;少数地主和企业家站在同一边,其他没有组织的、地位平等的无产阶级大众站在另一边——中间没有其他人。因此一般大众仍相信,只要消灭那群拥有一切的少数人,便可建立平等的无阶级社会。但两者之间缺乏中产阶级的原因,并不是社会已经完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完整循环,而恰是因为资本主义根本还没开始。这就说明了社会主义革命为何会与所有马克思主义的信条截然相反,不但没有发生在欧洲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反而会在最落后的国家出现——如俄国,根本就没有可套用马克思主义规则的经济和社会实体。它也解释了为什么俄国革命会违背共产主义领袖的期望,没有立即引爆西欧和中欧的革命——照说那些才是该革命的地方。即便是能力最强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也无法了解自己的形势。几乎整个西元1917年下半年和1918年初,列宁和托洛斯基都坚信,一旦俄国点燃引信,德国和奥地利的民众都会起身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信心满满,以至于冒着德国大军压境的风险,还迟迟不与德国进行谈判,甚至还坚持(托洛斯基至今还这么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发生只是偶然——几乎可算是错误,而在奥地利和德国的革命才是计划中、有必要且有意义的。
曾经是欧洲宪兵的俄国算是最落后的吗?这里姑且不论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俄国、中国都是因为没及时建立起有序的秩序而被摘了桃子赤化成为文明洼地,这和什么资本主义根本还没开始的鬼扯毫无关系。拿了威廉二世那么多德国马克的列宁居然不能满足金主的要求及早和谈,职业道德显然有限。中国对外援助也要重视这个问题。
“资本主义气数已尽”这话似乎是老生长谈了。然而,为支持这句话而常常提出的论点:“资本主义是失败的经济制度”,不仅暴露了说话者对这套制度全然无知,更可能是谬误。拜这套经济制度之赐,不仅商品生产量愈来愈高,价格愈来愈低,工作时数更不断减少;由此看来,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失败,更缔造了超乎想象的成功。从经济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的功绩实在没有理由不能名列于殖民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工业化之前。
资本主义气数已尽本质上来说是末日审判即将来临的一种变种,老狗玩的都是老把戏!
资本主义发展了一百五十到两百年,我们也到达物质经济舒适的高峰。也许因为这样,一听到“尽管我们全靠经济自由才能拥有这些成就,但它本身绝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句话,就想会加以嘲弄。但在饱受旧资本主义秩序戕害的人,在那些可怜的工匠、饥饿的农奴眼中,情况并非如此。对他们来说,经济自由只会带来恐惧,它要求他们放弃保障;就算只是悲惨、了无意义地保障他们不于至挨饿,也是他们唯一仅有的东西。经济自由不能给予他们任何经济上的承诺,只带来了不安。它夺走了他们小小的世袭土地、保护市场的关税,以及同业公会低到不能再低的价格,又叫他们以技能和智慧谋生。他们之所以接受这种自由,只因为相信它会带来最终社会和经济平等的保证。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经常起身反抗自己已获得解放的事实。对于实行经济自由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自治,有一条坚强反对的阵线。反对最力的一定是原本应该受惠最多的阶级,譬如:英国的勒德分子(Luddite)、爱尔兰农民的“小麦暴动”(Corn revolts)、德国西里西亚亚麻织布工暴动,以及俄国农民在西元1906年斯托雷平(Stolypin)土地改革后的骚乱——那次土改以经济自由与经济发展之名,把俄国乡镇的公共农地改为个人保有地。在这些实例中,反对势力最后得以弭平(不论是用和平或武力的手段),都是因为资本主义提出了要建立平等的承诺。
打土豪、分田地始终是左衽的必备技能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自由和结果平等显然是不兼容的,左衽的辩证法对此也无能为力。
卢德主义者(英语:Luddite ),或译勒德分子、卢德分子,是西元19世纪英国民间对抗工业革命、反对纺织工业化的社会运动者。在该运动中,常常发生毁坏纺织机的事件。这是因为工业革命运用机器大量取代人力劳作,使许多手工工人失业。后世也将反对任何新科技的人称做卢德主义者。西元1779年英国莱斯特一带一名名叫内德‧卢德的织布工曾怒砸两台织布机,后人以讹传讹成所谓卢德将军或卢德王领导反抗工业化的运动,遂得此名。今日鼓吹ChatGPT让人类失业的人宏观意义上也算卢德分子。但其实很多岗位消失的同时又有很多新岗位产生比如程序员失业后还可以去送外卖开滴滴,哈哈!
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不平等,但却比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以及共产主义者的祖国——苏联更接近平等,这就好比儒家学说不讲自由平等,但真正按照儒家学说运行的中国社会却比任何社会都更加自由、更加平等。
这场失败在经济领域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它使政治生活的一切制度都失去意义,或是令人怀疑。但它最深刻的影响反映在所有社会据以建立的基本概念上:社会中的人所具有的本质、功能及地位。个人的经济自由不会自动造就平等,这个事实已经摧毁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据以建立的有关人类本质的概念:经济人(Economic Man)。
每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都立基于一种概念,一种涵盖人的本质、社会功能与地位的概念。不论这个概念是不是人类本质的真实写照,都一定会真实反映出社会的本质,而社会也依此概念来辨识、鉴别自己。这个概念呈现出它认为社会中具决定性且最重要的人类活动范畴,并以之作为社会基本原则和基本信仰的象征。例如把人视为“经济人”的观念,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和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真实的象征;这两种社会都认为,人类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方法。似乎只有经济上的满足,才是对社会重要且有意义的事。人们工作是为了经济地位、经济特权和经济权利。为此人们发动战争,不惜牺牲生命;而其他所有的似乎都只是伪善、势利或浪漫却意义没东西的罢了。
经济人的概念,在亚当·斯密(AdamSmith)及其学派的“经济人”(homoeconomicus)中首度化为文字出现。经济人是他们虚构的角色,奸诈狡猾、不择手段,永远都以最大经济利益作为他的行动依据,也总是知道该怎么做。这样的观念虽然可以用在教科书里,但若用来描写人类的真实本质就太粗鄙、太夸张及滑稽了。连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也采纳马克思改良订正过的经济人版本:在此最后的分析中,经济人会倾向于依据“阶级利益”而行动,即使他无意这样做或不知道自己已经这样做了。
人不总是理性了,理性人假设只是个假设。行为经济学就是研究人的非理性行为的经济学分支。同样,人还要获得有尊严有精神追求——自我实现,而不能像小粉红那种反人类分子能吃能睡就咸恩心心了。不过说马克思主义社会认为人类自由从事经济活动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如果马克思主义证明它无法带来自由平等的社会,经济人的社会就难逃崩解的命运。因为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主张能够既赋予经济领域至高无上的地位,又相信自由和平等是社会的真正目标。而经济人或所有由经济人组成的社会,存在的唯一正当理由的基础,就是实现自由平等的承诺。
德鲁克本质爱马,显而易见。赋予经济领域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是为了控制信徒乃至于控制一切的基础罢了,宣传要实现自由和平等是社会的真正目标无非是为了找点信徒当炮灰,由此可见,德鲁克确实不懂什么是极权主义的起源。
相信人皆自由及平等,是欧洲思想的精髓。这个基本概念从古希腊城邦及罗马帝国时代便已潜伏,说明了我们何以对这此年代产生亲切感,一种当代南美洲等地不会使我们产生的感觉。随着基督教兴盛,自由与平等成了欧洲的两大基本概念;它们就是欧洲的代名词。两千年来,欧洲所有制度和信条都源自基督教秩序,且都以由目平等为目标,也以“最后一定会实现自由平等“的承诺作为存在的正当理由。因此,欧洲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将自由平等的概念,投射到社会存在现实上的历史。
鼓吹人皆自由和平等,显然是法国大革命前后才有的思想。毕竟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奴隶主和奴隶能平等吗?奴隶有自由吗?基督教会统治的中世纪卖赎罪券的主教和买赎罪券的信徒能平等吗?封建领主和农民能平等吗?农民有信仰自由吗???这种胡说八道以后不反驳了。一种当代南美洲等地不会使我们产生的感觉?那美国能不能让你产生这种感觉呢?可笑。基督教显然和自由平等不兼容,就像共产主义和自由平等不兼容一样,如果兼容,那只是宣传工作特别到位罢了。
欧洲人首先在心灵层面追求自由与平等的实现。基督教教义说,死后的世界人人平等,而且依据是此世的行为思想来决定彼世的命运(所以,此世不过是为死后的生命做准备)。西元18世纪人士和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这可能只是当时教会用来控制群众的手段而已,但对11世纪或13世纪的人来说,基督教的这个诺言却是真实的;每座教堂的大门都刻有教宗、主教或国王在最后审判日遭到天谴的图像,这可不是叛逆石匠们的浪漫幻想,而是真实表现出从心灵层面寻求自由平等的历史纪元。当时以“灵性人”(Spiritual Man)的概念来看待及理解人类,而人在世界和社会中的地位,则被视为在灵性秩序中的地位。如此一来,神学成了一门精确的“科学”。
每座教堂的大门都刻有教宗、主教或国王在最后审判日遭到天谴的图像?德鲁克你咋知道的?你看过了吗?就说所有,直接胡扯,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或者你根本没有良心?中世纪神学是什么玩意,你读过没有?塔尖上能站两个鸟人(angel)吗?这能是精确的科学吗?
至于用此世的贱命换来世的幸福,纯属神棍意淫。
儒学之所以不是宗教,就是因为只专注于现世,而从不售卖彼岸天堂的门票,在世界思想体系中实属良心过分。因为这样一来,做人就要正视现实,而无法用虚幻的梦境欺骗自己,而这是很多人心理难以承受的。所以儒学舍生取义的勇气是宗教信徒殉教无从企及的,因为儒学清楚自己要付出的是自身的一切,而后者却自以为能用现世的贱命换来幸福的永生,所以任何宗教以及与宗教无异的极权意识形态,本质上都是懦夫,他们就象靠喝酒吸毒才能壮胆的怂包一样,勇气与宗教从来无缘,宗教有的只是靠愚蠢支撑的狂热。同样原因,儒学行善的内核也与宗教信徒有着本质区别,宗教理解的行善是存钱,是交换,总之是与神灵之间一本万利的交易,或是被神灵威逼恐吓下的习惯性被迫,总之都不是自觉自发的行善。而儒学则把行善当成自我完成,是熏陶自身人格。从根本上,儒学是不相信善有善报这回事的,但求无愧于己而已,而并不会对没有回报失望报怨,就象孔子对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的评价,“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不得不说,没有相当强大的内心,很难接受儒学这种极度阳刚的思想。我们普通人,可能只有靠对未来或来世的期盼才能压倒对现实的不满和失望,也都期待付出必有回报,但儒学告诉你:没有来世只有现实,人必须在现实中尽责于家庭和社会,而现实只能靠自己努力支撑,努力也未必有回报,但只要你在这过程中完善了自己,就能自得其乐,无怨无尤。试问几人能做到?
当这个灵性秩序崩溃后,自由与平等转而投射至智识层面。路德教派“人的命运取决于他如何用运自由与平等的思维来解释《新旧约全书》的教义,正是智性人(intellectual Man)秩序最重要的变形——尽管不是唯一也不是最后一个。在智性人秩序瓦解后,人类转而在社会层面寻求自由与平等,结果,人先变为“政治人”,后来又成了“经济人”。所谓的自由变成社会自由与经济自由,平等也局限于社会平等与经济平等。人的本质就等于他在社会与经济秩序中所居地位的功能;在社会与经济秩序中,才能找到对人类存在的解释,以及存在的理由。
这种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中达到高潮。自由平等能在经济领域实现的信仰再次被提出,并建立于资本主义无达达成此目标的失败上。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就是实现无阶级社会的保证,因为它证明了,平等是不可能透过经济领域的和谐来达成的,民主制度除了形式以外一事无成(换言之,它是不平等的),也“证明”世人对真正自由的社会有多么迫切的需要。群众的贫困(或说地位愈来愈不平等),就成了获得平等和财富的媒介。纵观整个历史,就等于一部阶级斗争史,这证明了历史必会导向无阶级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有史以来所产生的最宏伟、最深奥的信条。只要资本主义秩序幸存于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最锋利的批评。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仰赖自由概念的辩证运用,而这几乎与放弃自由无异。马思思主义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一样,也认为社会的最终目标是确立真正的自由。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重视自由;然而为了证明人可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自由,马克思不但必须否定人在资本主义下是自由的事实,甚至还得否认人有自由的能力。社会主义的承诺立基于经济法则的自动论(automatism),但经济法则会剥夺人的自由意志,使人受特定阶级约束,也就是不自由。这跟加尔文主义一方面主张人有真正的自由、一方面又主张绝对宿命的矛盾一样,都是一种大胆的纯思辩神学(相对于经验神学)。的确,马克思主义和加尔文主义不管在思想上、意识形态上和历史功能上,都有显著的相似之处。
德鲁克居然能看到这点,我十分震惊!这刷新了我对他智商的认知!
社会理性特质的瓦解,以及个人与社会间理性关系的崩溃,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革命性的特征。在西方文化领域之外,非理性才是人类存在和人类社会中的常规;理性化就算真要运用,也会局限在非常狭小的范畴,如部落或家庭。但欧洲(也只有欧洲)却顺利挑战了整个宇宙的理性化。针对整个世界(人世和另一个世界)提出理性的解释,并为每个身处这个理性秩序的个体提供一个明确的空间(无论是在救赎的神圣计划,或人造的无阶级社会中),已成了基督教最形而上的成就,让欧洲与其他地方迥然不同。在其他地方,恶魔的力量在理性秩序之外漫游;它们 可以被召唤或安抚,但不能被理解,也不会发挥理性层面的影响;它们只遵循自己的规则。唯有欧洲可以驱逐它们、摧毁它们。当然,我们也有恶魔。只不过恶魔的力量是高度理性的;如果不把它们也视为世界的一部分,世界的意象就可能不被了解。连马克思主义都必须把资本主义者描绘成恶魔,虽然马克思本人一直努力想证明它们并不邪恶,只不过是公正经济力量的工具。与之相较,长着蹄、角和尾巴的撒旦,正是一场理性打败混乱的胜利。但是,一旦恶魔有能力在欧洲获得完全立足生活的权利,不论是希腊的森林女神或斯瓦西里的雨神,在我们的世界中都无立锥之地了。
撒旦确实是各路神棍反对事物的统称!
第三章 惡魔再現 The Return of The Demons
工业社会的现实也是不平等的。战争所奋斗的理想之所以无法实现,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经济人社会的理想与概念,与它被战争暴露出来的实际架构间,出现根本、彻底的分裂。但是这种歧异就足以摧毁我们对民主的信念。一些新的词汇如“穷国”(have-not)对抗“富国(have)这类常被用来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投射到国际关系上的用语,不但全然否定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强调的平等,同时也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阶级国际的团结”。
阶级斗争实质上是屠杀”异教徒“,30年来最著名的阶级斗争就是卢旺达大屠杀。
最后,自由的观念也遭贬抑,价值大不如前。因为事实证明,经济自由不会造就平等。经济自由的本质(也就是依据个人最大的经济利益来采取行动),已经失去了过去曾有的社会价值。不管优先考虑个人经济利益是不是人真正的天性,因为无法促进平等,大众已不再认为经济行为本身对社会有益。因此,如果有可能稍微远离失业威胁、经济萧条危机和亏本的风险,人们是可以接受甚至十分乐意削减或放弃经济自由的。
一般的地球人都这样,哎!
如果放弃自由就可以重建世界的理性秩序,大众已经做好了放弃的准备;如果自由和平等不兼容,他们会放弃自由;如果自由和安全无法共存,他们会选择安全。既然获得自由对驱逐恶魔毫无帮助,那么,要不要自由就成了次要问题。既然“自由”社会是受恶魔威胁的社会,那么,把问题归咎于自由、认为只要放弃自由就能走出绝望,就似乎相当有理。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著名人类自由的捍卫者显然会放弃”平等“(民主)而拥抱自由的!
第四章 基督教教會的落敗 The Failure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精英的中最后一位独立的欧洲思想家。他曾积极倡言这两种秩序的末路,到临终前都受到强烈的质疑。在他去世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新的一代,在社会思想领域都未再孕育出任何一位独立又有创见的领导者。列宁是两位最重要的追随者之一,虽然他在行动领域称得上独创、优秀,却刻意将智识活动局限在评论和校订大师的理论。另一位最重要的追随者是索雷尔,他试图承袭马克思主义信条在智识上的发展,最后却全盘否定其信仰内容、全面放弃自由人的观念,更将自发性的暴力尊奉为神。
穆勒也算马克思主义精英,这确实是个新发现。
乔治·欧仁·索雷尔(Georges Eugène Sorel)
西元1847年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学习过土木工程。1892年,他离开民政工程职务,专心于思考和研究问题。1893年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写分析和评论文章。1897年,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为德雷福斯辩护。1902年,他公开抨击当时主流的社会主义和激进党派通过民主和宪政通往社会主义的设想,并热切支持革命工团主义。在索雷尔看来,民主制度与其普选权及政治统治权,最终只会加强劳工阶级在经济上被奴役的程度。1909年以后,他对工团主义逐渐失望。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宣布支持布尔什维克,他认为布尔什维克能使人类在道德上再生。索雷尔的哲学结合了柏格森和尼采的思想,认为理性受制于感性。这成为了他创立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他认为,通过动员非理性力量进行暴力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方式。索雷尔将总罢工赋予一种神秘色彩,认为它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可以动员工人采取“英雄式的暴力”,并进而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和一些民粹主义者不同,索雷尔眼中的社会主义是由少数精英治理的。索雷尔认为,一般大众不具有控制自身的能力,因而只能被精英统治。他的思想对后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有很大影响。
第五章 極權主義奇跡?——以意大利和德國作為實例 The Totalitarian Miracle: Italy and Germany as Test Cases?
希特勒的情况也和墨索里尼类同。希特勒和后者不同的是,他是一位典型的革命家。他个人过着苦行生活的这点特质,证明了他对革命的执着,一如墨索里尼纵情欢乐、跟男孩一样爱胡闹的性格,表示他是热爱权力、只为自己着想的人。然而和墨索里尼相同的是,希特勒也希望运用现有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来达成他个人的政治目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经济问题没什么着墨,这表示他深深相信自由竞争、个人的创造精神和政府不干涉经济是好事情,仿佛是亚当·斯密最坚定的信徒。希特勒也和早期的资本主义者一样相信所有阶级能在经济上达成和谐。因此,他确信只要除掉“垄断”与“金融资本主义”等四处攫夺的势力,商业就可以透过代议机关来自我管理。我曾亲耳听过希特勒抨击拉特瑙与其弟子,因为他们主张极权化的经济体制——依照希特勒在西元1931年的说法,这将使得国家成为社会结构下的奴仆。
由此看来,希特勒其实是反对经济和社会的极权主义的。当他的手下沙赫特与整个纳粹党唱反调时,也只有他本人力挺到底。希特勒否决了将德国银行整并为一的计划,并下令政府将在经济萧条时期不得不接手的银行与企业股份,重新转售给社会大众。这种重新私有化的方式最后丝毫未能动摇纳粹政府对各行各业的掌控,并不是希特勒的错。在人民因为民主秩序内涵消失而放弃了对这种秩序的信仰之际,希特勒也不得不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人民的绝望逼使希特勒迈向社会革命之路,这不仅夺去他政治革命的光彩,也迫使他必须彻底修正外交政策。
这确实是个新观点,值得日后考证。
第六章 法西斯主義下的非經濟社會 Fascist Noneconomic Society
在意德这两个法西斯国家施行的农业组织化,是第一个也是最激烈的一个干预经济力量自由发挥的手段。
极权主义的经济被认为是个神话。人们也常用“奇迹”两字来形容它。事实上,它非常简单、非常理性、没有丝毫神秘可言。它是极权主义体系中逻辑最严谨的一部分,因为它完全建立在最正统的经济理论上。它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差异,在于它的所有经济目的都附属于一个社会目标:充分就业。经济进步与财富增加,都是附带的产物。
极权主义经济基本的“创新“,很反常地,就是回归古典经济学最根本的宗旨:唯有增加生产资料的投资,才能创造就业机会。这或许听来有点老套,却是对现代经济理论最直接、最坚定的反驳,依后者的宗旨而言,经济活动就等于消费。纳粹在掌权之前就曾正式采纳过现代的”消费不足”(under consumption)理论——认定经济萧条肇因于缺乏购买力。然而,现在他们的整体经济政策,却立基于完全相反的观点:经济萧条的起因是消费过多、对产品制造业投资太少。由此他们导出这个结论:要恢复充分就业,唯有增加国民收入在“储蓄”(而非被“消费”)方面的定额。这意味着,可用于消费的限额必须透过人为手段压低。极权主义经济的一大奥秘在于“管制性消费”(managed consumption)。他们成功压低了消费量,因此似乎得以“创造”出资本,用以投资生产资料生产;相形之下,民主政治用尽所有剩余资本,却无法透过提升民众消费量与购买力的手段,来达到充分就业。、
这种管制消费的理论方法与施行方式,均非极权主义原创,而是几乎原封不动地沿用苏联的经验。
古典经济学最根本的宗旨?这块存疑。
在极权主义社会中,经济上的牺牲不仅提高社会地位,还增强了指挥社会的权利与权力。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矛盾:主张经济平等的共产主义,却必须赋予某些人经济上的特权;而极权的法西斯主义,虽然保留了现有工业生产的不平等制度,却大幅降低了特权阶级的生活水平,以建立一个人追求经济平等的明显趋势。
第七章 是奇跡,還是海市蜃樓?Miracle or Mirage?
法西斯憎恨共产主义,正表示它无法战胜法西斯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因为人们不能接受军事国家的意识形态,阶级战争就不可能废除。除非人们相信阶级斗争是与法西斯理想与承诺中的非经济、真正无阶级社会敌对的势力,才可能予以禁止。唯有把阶级斗争拟人化成共产主义者,才能与之抗衡;法西斯必须把社会产生邪恶势力的责任推给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不需提出证据证明共产主义有所行动。德意志共和国末年或战后意大利是否真的受到共产主义威胁,根本无关紧要。在共产主义者洗脱纵火焚烧德国国会大厦的罪名时,纳粹元帅戈林(Hermann Goering)就坦言:就算所有证据都显示共产主义者是无辜的,德国人仍会坚定地认为,他们是这起纵火案的罪魁祸首——他补充说,这是因为“我们知道,敌人一定不是德国人民”。为了证明自身的存在、找到存在的理由,法西斯主义必须不断强调共产主义图谋不轨,不断强调莫斯科和其他法西斯的敌人(包括英国银行家、捷克军队、罗马教会和精神分析学家)为打击法西斯而结盟。
这显然是因为同行是冤家!
以组织之名,法西斯必须废除一切个人权利及自由、摧毁所有真正的社会单位,如家庭、青年团体、学生会、政党、职业协会等。
这些都是打造原子人的常规操作!
这位“领袖”只有肉体是人;在精神上,他不像人类会出错,超越了人类的伦理道德、超越了人类社会。他“永远是对的”,从不犯错。他的意志决定了善恶;他的地位凌驾于社会之上,不需仰赖社会支持。唯有如此,极权主义社会的紧张状态才能为人们所容忍。唯有盲目而毫不怀疑地信仰领袖,人们才能获得信念的安全感——这是极权主义信条无法赋予又不得不赋予的。 …… 因为法西斯独裁者的主要“职责”,是运用个人恶魔般的群众魅力来拯救社会。德国的新教徒农夫常在原来悬挂耶稣像的地方挂上希特勒的画像,这绝非偶然。纳粹的支派,如“德国基督徒”,都很清楚:他们心中的领袖(人神神性),是世俗化之后的救世主。
“希特勒永远是对的”和“墨索里尼永远是对的”,就是这种神秘主义的基本教义。只有毫不怀疑地相信他们,才会觉得世界和社会是理性而且可以容忍的,只有墨索里尼或希特勒,才能使必要的极权主义信仰成为可能。信仰这些教义,就是精神信仰的真正本质——这是一种超脱理性范畴的经验,不容批评或讨论。
准确来说党中央是永远伟大光明正确的!
今昔相似之处甚至可以延伸到以下的细节。加尔文主义之于智性人社会,就如同马克思主义之于经济人社会:两者都宣称自己的信条就是救世主。两者也都相信唯有牺牲真正的自由,才能达到自由和平等。加尔文主义借着宿命论确立教义,一如马克思主义透过阶级状况来确立原则。两者都在当时社会废除了真正的自由,好让人们继续相信,自由马上就要在即将来临的社会种获得实现。然而,当事实证明他们只能实现一个不自由的社会后,这两种主义,这两种秩序,也就彻底崩溃了。
德鲁克能看到这点,也算有点眼光,虽然全篇胡扯为主。
第八章 未來:東西對抗?The Future: East Against West?
事实上,期待苏德开战的想法,绝对只是一厢情愿。除非意外介入,否则苏德成争是打不起来的。……
苏联和德国将来必会比肩而行,因为它们在意识形态和社会上都非常相似。欧洲左派不敢承认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若是承认苏联跟德国一样也是法西斯国家,就等于承认社会主义终将失败,也就等于抛弃了自己。但闭上眼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相反,就是这种不愿承认现实的态度,让他们什么事也做不成。至于右派政党,他们知道苏联的本质和德国雷同。因此,他们不愿做出这样的结论,甚至还坚持“苏德必将一战”的说法,就更不可原谅了。只能说(但不能以此)为借口),是绝望让他们如此自欺欺人,让他们期盼奇迹出现。
事实上,德鲁克错得很离谱,这点不说了。还是那句话,同行是冤家!
在列宁逝世、苏联以新经济政策取代了原本的五年计划后,共产主义就已名存实亡了!
新经济政策难道不是列宁活着时推行的吗?苏联的情况那么不了解吗?
更重要的事实是:这些“坚定的极权主义者”均出身于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学派,几乎无一例外。拉特瑙是犹太人、左派民主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手掌握德国原料,在外交部长任内被纳粹刺杀;他也是鼓吹极权主义经济的第一人。拉特瑙没有预见极权主义经济会走向法西斯主义,相反,他以为极权主义经济是迈向自由平等的最后一步。
各种各样的反犹主义盛行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如果极权主义赢得这场战争,欧洲将会经历一段黑暗与绝望交加的漫长时光,一如西元13世纪和16世纪的“极权主义”时代,原有的欧洲秩序彻底崩溃。极权主义最终一定会自取灭亡,而一个立基于自由平等的新秩序,会从极权主义笼罩的黑暗中出现。
附录:极权主义的表征
数学到底是不是种族主义?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我认为没有必要讨论。
宣称数学是种族主义的某些人的别有用心,倒是值得深究。
在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之前,你必须认识到一个基本事实:
共产主义是现代的基督教,是自诩理性的左派知识分子的启蒙福音。
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组织形式类似于中世纪天主教会/伊斯兰教哈里发国,其他一般左派政治运动的组织形式类似于现代新教教会。
按照基督教教义,人在被亚威创造之初,活在伊甸园里。"亚威在东方的伊甸,为亚当和夏娃造了一个乐园。那里地上撒满金子、珍珠、红玛瑙,各种树木从地里长出来,开满各种奇花异卉,非常好看;树上的果子还可以作为食物。园子当中还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还有河水在园中淙淙流淌,滋润大地。河水分成四道环绕伊甸:第一条河叫比逊,环绕哈胖拉全地;第二条河叫基训,环绕古实全地;第三条河叫希底结,从亚述旁边流过;第四条河就是伯拉河。作为亚威的恩赐,天不下雨而五谷丰登。亚威让亚当和夏娃住在伊甸园中,让他们修葺并看守这个乐园。亚威吩咐他们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死。"亚当和夏娃赤裸着绝美的形体,品尝着甘美的果实。他们或款款散步,或悠然躺卧,信口给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取名: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园中的嘉树;田野的鲜花。他们就这样在伊甸乐园中幸福地生活着,履行着亚威分配的工作。他们因受蛇的引诱违背亚威的命令吃了伊甸园的禁果,而被亚威惩罚。蛇“必受咒诅”,从此要用肚子行走及终生吃土;后裔要与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它的头,而它则要伤她们的脚跟;(创 3:14-15)女人怀胎的苦楚加增,生产时要受苦楚;要恋慕丈夫,及被丈夫管辖;(创 3:16)男人则要受咒诅,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他归了土;从此需终身劳苦才能从(田)地里得到食物,而地会长出荆棘和蒺藜(创 3:17-19);"人类被亚威逐出伊甸园,必须赎罪可能得救。得救之日,将有末日审判:千禧年结束后,基督和圣徒并圣城新耶路撒冷要重返地球,有天使陪同,当基督在极其显赫的威严中降临的时候,他要命令那些失丧者从坟墓里复活接受报应,那些各国各代没有得救的人都复活了,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基督的脚将踏在橄榄山上,随之而来的大地震将山分裂成为极大的谷,圣城新耶路撒冷就降在这里。看到那么多以前跟随过自己的人全都复活了,撒旦就死灰复燃进行最后的争斗,他决心要顽抗到底,他命令那些复活后的失丧者用武力去攻占圣城。在关键时刻,基督升到了圣城的上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开始了,当案卷展开,基督的慧眼定睛于失丧者的时候,他们立刻感悟到自己犯下的每一项罪恶,他们看出自己如何拒绝基督和他的救恩,如何藐视神的使者,如何干犯他神圣的律法,如果罪没有被羔羊的血涂抹,就会被公开回放,成为世人皆知的事。在那些失丧者中有傲慢的教皇,他们曾高抬自己超过神,甚至自称是神,并擅自篡改神的律法,还有虚伪的神父和主教们,他们曾经用残酷的刑罚来统治神的子民,他们最终都要向神作交代。全体失丧者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为他们反叛上天的政权受审,他们必承认神对自己的审判是公义的,于是有永死的判决宣布在他们身上。当宣判结束后就有火与硫磺从天降下,地面裂开炙热的火焰从地底涌出,当失丧者和撒旦及堕落天使被地狱之火吞没的时候,得救的圣徒在圣城里得蒙保守而安然无恙。每个人的量刑程度都要按照自己所犯的罪的轻重决定,罪较轻的人很快被火烧灭,犯下可怕罪行的人要多受煎熬,而撒旦一切罪恶的魁首自然要承受最大的痛苦。刑罚恶者对于慈爱的神来说是痛苦的,但他必须彰显公义,别无选择,罪的刑罚就是死亡,十字架上耶稣为所有信他的人承受了这最后的刑罚,但那些失丧者却拒绝了这白白的救恩,就不得不自食其果,为自己的罪恶付上可怕的代价。当刑罚罪恶的地狱之火最终熄灭后,全宇宙的公民都要欢呼赞美神,被撒旦奴隶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罪已经永远的消失了,整个宇宙有了永远的和平与安宁,神可以开始专注于创造新天新地了。所有信士义人将在天堂里永远幸福的活下去:第三层天是神的住所,它的位置没有被揭示。耶稣应许要在天堂为真正的基督徒准备地方(约14:2)。旧约圣徒相信,天堂是作为救赎主的神应许他们死后的归宿(弗4:8)。无论是谁,只要信基督就永不灭亡,反得永生(约3:16)。使徒约翰蒙恩看到了天上的城邑并对它作了介绍(启21:10-27)。约翰见证了天堂(新地)拥有“神的荣耀”(启21:11),即神的存在。因为天堂没有夜,主自己就是光,不再需要太阳和月亮(启22:5)。城中充满了昂贵宝石和明如水晶的碧玉的光辉。天堂有十二个门(启21:12)和十二个根基(启21:14)。伊甸园般的乐园得到了还原:自由流淌着生命水的河与生命树得以重现,生命树每月都结果子,它的叶子能“医治万民”(启22:1-2)。但无论约翰如何善于描绘天堂,天堂的实际情况远远超过了有限的人的描绘能力(林前2:9)。天堂是个“不再有”的地方。在那里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疼痛、不再有悲哀(启21:4)。在那里不再有分离,因为死亡将被战胜(启20:6)。天堂里最美好的就是有我们的救主(约一3:2)同在。我们将来可以与神的羔羊面对面,因为他爱我们并为我们舍己,让我们能够在天堂永远享受与他同在。
嗯!?这些桥段看着怎么有点眼熟?这不是花花主义乌托邦吗?
人口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人们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情商,道德水平极大提高,远离并逐步消灭掠夺、侵略、欺压、暴力、犯罪 、恐怖和一切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消除宗教产生和传播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宗教走向消亡 ,科技极大进步,教育极大发展,文明极大普及,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时间不断缩短。 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工农之间、 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差别消除,劳动不再是旧式分工中的劳动,不再具有强迫性,成为发挥人的才干和力量的活动,人生快乐的源泉和动力,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 ,每个社会成员获得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让我们看看社会主义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先驱是怎么说的:
在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社会主义未来中:
所有有害的野兽都不见了,它们的位置被帮助人类劳动——甚或替人工作——的动物所取代。人们可以看见一只“反河狸”在捕鱼,一头“反鲸”平静地拖着帆船,一头“反河马”拉着河船。代替狮子的是“反狮”,这是一种快得惊人的战马,骑手坐在它们背上就像坐在弹性很好的马车里一样舒服。“生活在有这些仆人的世界中是一种乐趣。”
傅立叶说,大洋里将会装满柠檬水而不是盐水。
“村里墙上画着鲜艳的壁画:年轻人攀着刺破蓝天的玉米秸爬上天空;老汉乘着比船大的花生壳,飘洋过海,周游世界;嫦娥从月宫下凡,到农田采摘斗大的棉桃……县委书记汇报,今年全县平均亩产达到两千斤,总产量达到12亿斤。此外,还要放大卫星,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
“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大学,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河南方城县城关镇,共有人口1.1万人,在几个月之内就建起了综合红专大学、卫生、戏剧音乐、舞蹈及师范等九所专科学校。各种工农大学、红专大学,如雨后春笋,茁壮出生。”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给。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冷气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第四队二亩小麦丰产试验田,总产14,640斤,平均亩产7,320斤。这是河南省今年麦收中放出的小麦亩产3,000斤以上的第29颗“卫星”……这二亩小麦长的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1,486,200株,密得老鼠也钻不进地。最大的麦穗有130粒,一般的麦穗有七、八十粒,最小的麦穗也有50粒左右。”
“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7月1日,中科院宣布了300多项科研成果,“其中超过国际水平和达到国际水平的共有25项”,包括应用物理研究所研制成功当时世界上功率最大、频率最高的半导体晶体,超过美国同类产品,而且是在20天内突击研制成功的。
不到两个星期以后,中科院又宣布完成1000项科研项目,其中100多项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北京大学也不甘示弱,声称在半个月内完成了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3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科学技术,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半个月之后,北大进一步宣布3406项科研成果,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981项。所有项目都是在40天之内完成的。”
这些荒唐可笑的白日梦就是花花主义者的花花主义乌托邦的根基。
另外,在花花主义先驱口中,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
嗯!?
人怎样才能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机智的花花主义先驱早就帮我们想好了解决方案:
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写的,共产主义将给“每个人以在各个方面发展和运用自己的全部身心能力的机会。” 而列宁则在1920年期待“取消人们的劳动分工……用全面发展和全面培训来教育和培训人们,人们能够做一切事。共产主义正在迈向并且必须迈向这一目标,而且会实现这一目标。”
但是我们知道,就连时间也存在稀缺性。你不可能同时做两件事。 “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各个方面发展自己的全部身心能力,这个梦想只会鼓舞头脑简单者的幻想,它忽视了人类生命的局限所带来的限制。由于生命就是一系列选择活动,每一种选择同时也就是一种放弃。 即使是恩格斯的未来仙境中的居民,早晚也要决定他是希望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还是第一海务大臣(First Sea Lord),他应该努力做优秀的小提琴手还是拳击手,他应该选择了解全部的中国文学还是知晓鲭鱼生命中的所有秘密。”
我们伟大的花花主义先驱那么机智,怎么可能想不到这一点?
他们早就帮我们想好了解决方案:
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认为,一旦私有财产被废除,人类就会成为不朽之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尔·考茨基断言,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会出现一种新人……一种超人……一种高尚的人。”列夫·托洛茨基预言到,在共产主义制度下:
人会变得无比地强壮、聪明、出色。他的身体更加匀称,他的动作更加协调,他的声音更加好听……人类的平均水平会达到亚里士多德、歌德和马克思的水平。在此之上会出现新的高度和颠峰。
柯庆施作了一个关于文化“大跃进”的发言,其中在讲到15年后的中国的文艺时说: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不但有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而且工农兵自己也能更普遍、更高明地动手创造文学艺术,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人们不但可以经常看到电影,而且可以从电视里学科学、学先进经验,同先进人物会见,看到整个地球以至整个宇宙许许多多的新东西。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
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市、自治区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了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 根据8月北戴河会议精神,召开了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大跃进”中的文艺工作和迎接国庆10周年的文艺创作任务。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诸方面都要争取放“卫星”。文艺创作和批评都要大搞群众运动。据此要求,文化部成立了全国文化大普及办公室,一些省、市、区也成立了文化卫星指挥部,开始大放“文艺卫星”。很多地方提出了一些口号:“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立即修改了原定的“跃进”指标。原计划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1000件,现在改为3000件,原计划创作大型作品和重点组织的作品集120部,现增加到235部。可是不久,这一指标又被突破,被更改为: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4000篇,创作歌词3000首,完成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专著12部……
“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目前,农民绘画在我县已经形成了全民性的运动,农村中千军万马的美术队伍,日夜苦战,八一前统计:全县即有1800个农村美术组,6000多个美术骨干,7月份完成壁画23300幅,宣传张贴画15000幅,达到村村有壁画10幅以上,队队有壁画5幅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壁画县。8月3日县委在官湖召开了现场会议,又来了一个大跃进,至8月15日,全县农村美术骨干发展到15000人,完成壁画105000幅,宣传张贴画78000幅,达到50%的村社户户有壁画1-5幅。”“编者按”称赞道:“邳县的农民壁画运动是群众美术活动中的一颗‘卫星’。”“这是党的总路线的伟大作用在美术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我国革命美术事业向共产主义跃进的一个新形势,它的重大意义在我国美术史上是划时代的。”
先驱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到底有没有可行性,我们不做深入讨论。
我们要讨论的是宗教。
嗯。宗教。
“威尔弗尔则在一九三二年在题为“没有对亚威的信仰我们能够生存吗?”的谈话中对于流行的虚无主义、自然主义的信仰形式提出强烈的批评。在涉及到极权主义现象出现的问题的时候,他认为它是一种“替代宗教”,或者说“宗教替代物”。
“我们时代为青年人提供了两类激进型的信仰。您可能已经想到,我们那些在街上的儿子,一些个是 ,另外一些个是纳粹。自然主义虚无主义也同样分裂为两支。青年人无助地继续失去自我。 主义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成为最原始本能的战胜自我的出路。它们是一种替代宗教(Ersatz-Religionen,),亦或他们想要的是,一种宗教替代物(Religions-Ersatz)。”
一九三七年,奥地利的研究精神史的法尔尕(Lucie Varga)女士,在法国布洛赫和费弗尔主持编辑的《历史年鉴》上发表了有关政治宗教的论文,题为“纳粹主义的产生”(见《时代转折:1934-1939精神史研究》,115页)中,她使用政治宗教概念来描述了德国的纳粹运动。
“就在眼前一个旧的世界在完全走向结束,一个新的世界以一种至今人们所不熟悉的外形产生。” ;“老的钥匙无法打开新的锁”。
她在对德国那些纳粹追随者们进行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革命,这意味着一切都简单了,到处使用的是二元论:朋友或敌人,斗争的同志或者斗争的敌人…… 为此产生了对领袖和学说的盲目的狂热的信仰,一种完全的牺牲。”她分析了德国社会情况,最后得出结论,“在整个德国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教派都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纳粹极权主义的政治宗教和与之对立的神主宰一切的宗教。”
在同一年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她再次提到,在德国,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反对者不是新的异教崇拜、宗教上的半瓶醋们,而是纳粹,一种用暴力的福音教义代替神的神圣的政治宗教。
她在对德国那些纳粹追随者们进行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革命,这意味着一切都简单了,到处使用的是二元论:朋友或敌人,斗争的同志或者斗争的敌人…… 为此产生了对领袖和学说的盲目的狂热的信仰,一种完全的牺牲。”她分析了德国社会情况,最后得出结论,“在整个德国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教派都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纳粹极权主义的政治宗教和与之对立的神主宰一切的宗教。”
一九三八年意大利极权主义批评者斯图尔佐(Luigi Sturzo)提出,“ 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是宗教并且一定是宗教。”他认为,不仅是在外在的和形式上极权主义和宗教协调一致,而且在实质上也是交叉相叠的。它们造就了极权主义最本质的吸引力。(20)
跟随父母由德国移民到英国的著名记者福埃格特(Frederick Augustus Voigt,1892-1957)也在一九三八年出版了《归于凯撒》(Unto Caesar)一书(21)。这本书三百五十八页,中心思想是, 党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革命性的世俗宗教”,它产生于人的过分傲慢的要求。他们竟然想要把本来存在于宗教信仰中的承诺,直接地变成尘世世界中由他们所能给予的现实。
福埃格特明确地说,“我们把花花主义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都称为世俗宗教。他们不仅不是敌对的,而且在根本上是类似的。它们都具有带有世俗意义的宗教内容,它们都是弥赛亚救世主式的,都是社会主义,都拒绝一切在原罪原则下的基督教知识。这二者也都只是用阶级或种族来看待善和恶,他门在方法和精神上都是专制的。这两个社会都有加冕的凯撒,集体化了的个人,以及个人灵魂中不可饶恕的敌人。这二者都是把本来应该归于上帝的,归了凯撒。”
同样,在B52统治下的革命也不仅仅简单地是要重新恢复昔日辉煌、成为又一个中央集权王朝。恰好相反,伟光正的领导人是把他们自己更多地看作是一个改变世俗世界历史的工具。
他们所做的改变是要扫除掉以前的宗族统治,原来的地方和地区守护神,然后创造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并且最终到达天堂般的状态。从‘长征’开始B52就被图画、诗歌、祷告般的布道呼唤程式化为一位新的基督教式的救世主。在他的领导下消灭了‘黑暗势力’,并且‘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变化’。谁如果敢于反对这个新的太上皇,谁就会受到审判,最好的情况就是带上耻辱的帽子进行忏悔,而且要发誓改过自新。”
**对于这种现象,迈尔进一步指出:一个货真价实的对B52的太阳崇拜不仅在东方产生而且也在西方的文化革命中。B52在颂歌、庆祝会以及游行中被美化、神圣化。他的著述早就被供奉并且随时间推移而成为有效的典范。一九六四年,为伟光正士兵使用的出自“伟大的领袖”的话编辑而成的“红宝书”成为正式的类似于基督教教义问答形式的B52思想教义问答。在一九六六年到六八年间印刷了不少于七亿四千万册(其中包括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一亿五千万册,B52诗词九千六百万册,)。(15页)在这本书中,他进一步地指出,尽管B52和伟光正的领导人可能以前并没有读过《新旧约全书》,也没有进过教堂,有信仰基督教的经历,但是他们的文字风格,游行庆祝的形式,包括六六年产生的红卫兵及检阅红卫兵的形式,党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形成及会议形式,都是典型的基督教式的,是在中国传统中所没有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类似于“数学是种族主义,是白人压迫有色人种工具,阻碍有色人种接受高等教育的工具。”这样的,左派常用的平等主义话术,根本不属于共产主义的核心内容。
既然如此,左派为什么要把这些不符合正统教义的鬼话挂在嘴边呢?
这和左派政治运动的组织结构有关。
一切形式的左翼政治运动都有两个推手:
一是人数较少的,以救世主自居的左翼政治精英/左翼知识分子。
前者以高度中央集权的,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为代表;
后者以去中心化的,法兰克福学派,法国左翼存在主义,博厄斯文化人类学派的左派文科知识分子为代表;
这些人的性质类似于红衣主教/新教牧师。
他们认为自己是神的使徒,是弥赛亚福音的传播者,是降临人间的救世主/救世主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
耶和华拣选的牧羊人当然不可能和耶和华的普通羔羊平等。
亚威面前人人平等吗?
平不平等取决于革命需要。
但是基督教会不可能只有神职人员而没有一般信众。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总不能当光杆司令。
所以必须发动群众,主动传教。
因此,鼓吹平等主义,煽动流氓无产者的嫉妒情绪,制造普遍的受害者心态,很有必要。
左翼政治运动的第二个推手,就是被这一政治宗教的神职人员发动起来的一般信众——————各种形式的流氓无产阶级。
人生而不平等。
有的人天生就比别人漂亮。
有的人生下来就比别人聪明。
有些人的父母比别人的父母富有。
无论我们接不接受,这都是不能改变的的基本事实。
所以,你认为:
对于某些高考失败者来说,
是承认自己智商低比较容易接受?
还是把自己考不上大学归结为高中教育资源
缺乏比较容易接受?
(当然,如果你把他送到衡水中学去,他未必愿意接受衡水中学严酷的军事化管理。
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愿望是当工农兵大学生)
对于那些长得不漂亮而且超重的白人坦克女权主义者来说,
是承认自己天生长得丑,缺乏控制饮食的意志力比较容易接受?
还是指责主流社会审美观点有问题,存在瘦子对胖子的系统性压迫和歧视比较容易接受?
对于那些狭义的流氓无产阶级来说,
是承认富人的财产是他们应得的比较容易接受?
还是指责富人为富不仁,靠着撞狗屎运/丧尽天良才赚了大钱比较容易接受?
当你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以后。你就会发现:传统马克思主义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是一种宣传模板。
这一阶级斗争模板中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身份,按照具体历史情景和传教需要,可以被神职人员任意替换。
可以是男人和女权主义;
可以是白人和黑人;
可以是具有革命精神的red卫兵小将和反动学术权威;
可以是主流社会和性少数群体];
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一般来说,在革命运动中,高组织度的神职人员和天主教会对一般信众具有绝对的控制力。
流氓无产者发泄仇富仇强心理必须服从于党的政治需要;
但是凡事总有例外。
在某些去中心化的左翼政治运动中,流氓无产者的仇富仇强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受控制的。
所以有了白卷英雄张铁生。
所以有了工农兵大学生:
“我们高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
所以有了“数学是白人对有色人种的进行系统性种族压迫的工具”这样的怪谈。
红太阳之下,并无新事。
把个人利益同人民的利益相结合
前言
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是可以结合的,不是完全敌对的关系,比如牺牲自己也能为自己的后代或自己的名声增光。但一般情况下利己和利他是矛盾的,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只需要一小部分利他主义者。
至于马教徒伪装皇汉出来整活玩塔基亚,将来还是得制裁的!
正文
前文:
伊头鬼作:左翼政治思想的社会生物学基础61 赞同 · 12 评论文章
一个月以前,我回答了一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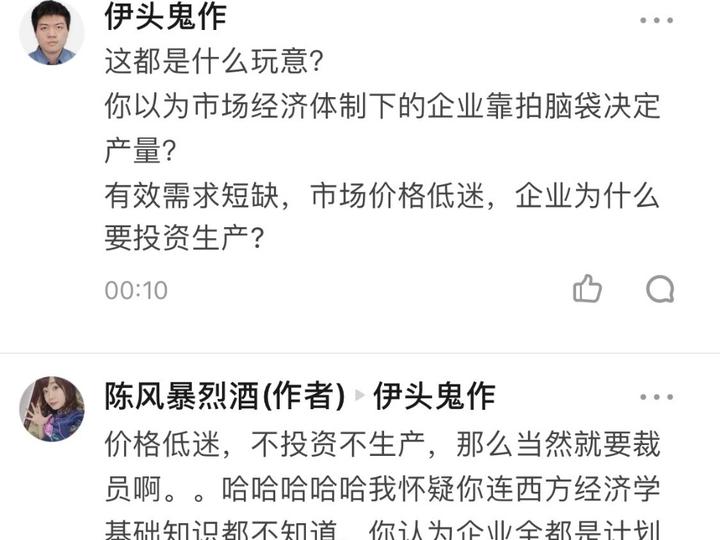
看到标题,
你就能明白,这根本不是在提问
这是一场 教徒的自嗨狂欢。
因为侮辱了B52,我的回答被续了。
我也懒得修改。
后来,有人告诉我,我的回答被很多人挂了。
还被一些马老爷扣上了精资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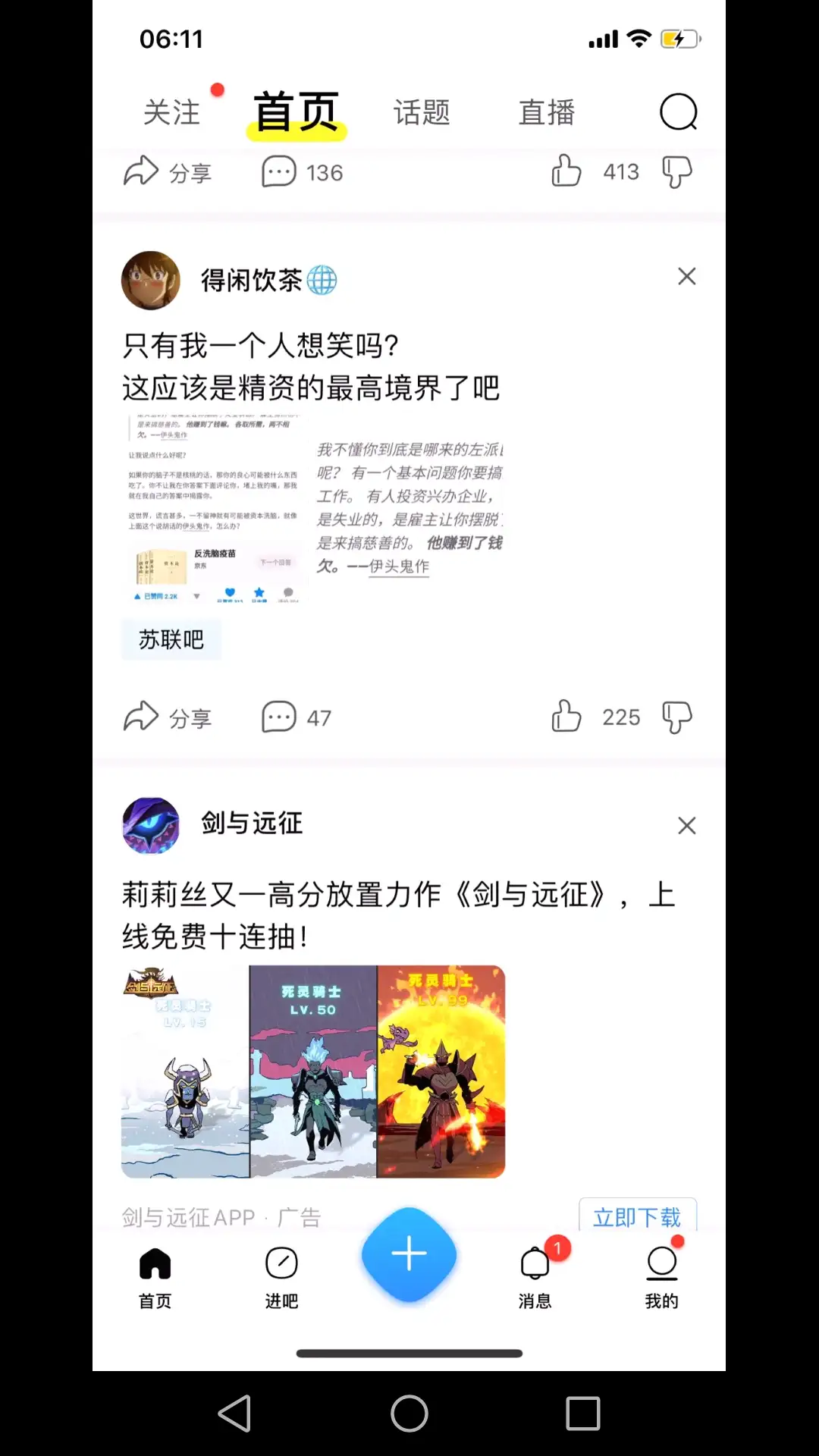
我:小农经济体制下存在大量的过剩劳动力。
在没有资本家的时代,他们本来也没有什么工作。
正是资本家的投资创造了就业,
而非造成失业。
教徒:你是精资。
这时,我有两种选择:
(1)我:我就是资本家的大少爷。
教徒:果然是屁股决定脑袋,没有背叛阶级的个人。
资本家的狗崽子为资本家张目,天经地义。
(准备开始发动借机斗争)
(2)我:我和资本家没关系。
教徒:你身为无产阶级,怎么能站在资本家的角度思考问题?
脑子都被资本家洗傻了!
表面看上去, 教徒的逻辑是无敌的。
教徒到底想要我干什么呢?
当我是资本家的时候,
教徒要求我:
不能站在资本家的角度,以利己主义为出发点思考问题。
要站在利他主义的,全人类的高度上,无条件支持mks主义;
当我不是资本家的时候,
教徒要求我:“坐对自己的屁股",反对资本家,支持马克思主义;
不要站在社会整体(利他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否则就是“精资”;
现在问题来了:
教徒一直在鼓吹:
“( 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嗯???
既然如此,
他们为何还要向他人暗示:
无产阶级必须“站对屁股”,发扬利己主义精神,反对资本家?????
看过前一篇文章,我们都明白:
资源总是有限的。
因此,我们总是面临着只顾自己和舍己为人的两难抉择。
在现实生活中,
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常常是相互矛盾的。
维护集体利益往往意味着牺牲个人利益,反之亦然。
伊头鬼作:左翼政治思想的社会生物学基础61 赞同 · 12 评论文章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信徒的眼里,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好像是没有矛盾的?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
左派人士……………善于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相结合。
寓个人利益于人民的利益之中,把个人利益转化为人民的利益。
善于把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统一起来:
“我们要打倒资本家,不是因为我们仇富。
是因为只会吸血的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
资本家里也许有好人。
但是,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的代表,必须被彻底消灭!
你要知道,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当马克斯主义者想到“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踏上去滚一滚”的时候,
他绝对不能说,“我想扒地主阶级少奶奶的床”。
他一定要说:"人民想到地主阶级少奶奶的床上滚一滚!”
当马克思主义者想恰烂钱的时候,
他绝对不能说;“我想恰烂钱”
他一定要说,“是人民想恰(烂钱)!”
当左派人士想扒老太太裤衩子的时候,
他绝对不能说;“我想扒老太太裤衩子”
他一定要说,“是人民想扒!”




“我做的这些事情,都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是为了人民!!!!(震声)”
“我是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的人!”
我们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震声)!
“我们是有道德的人!”
“我是这个世界上道德最高尚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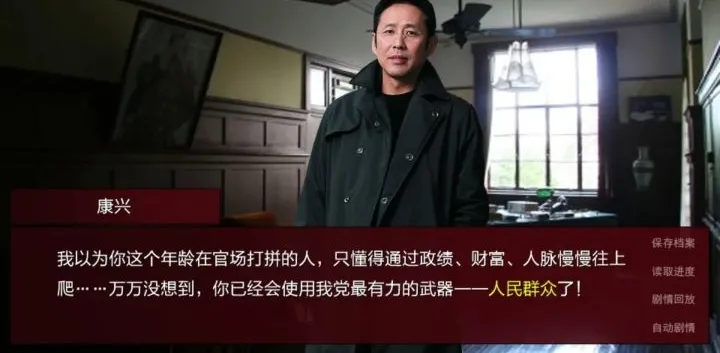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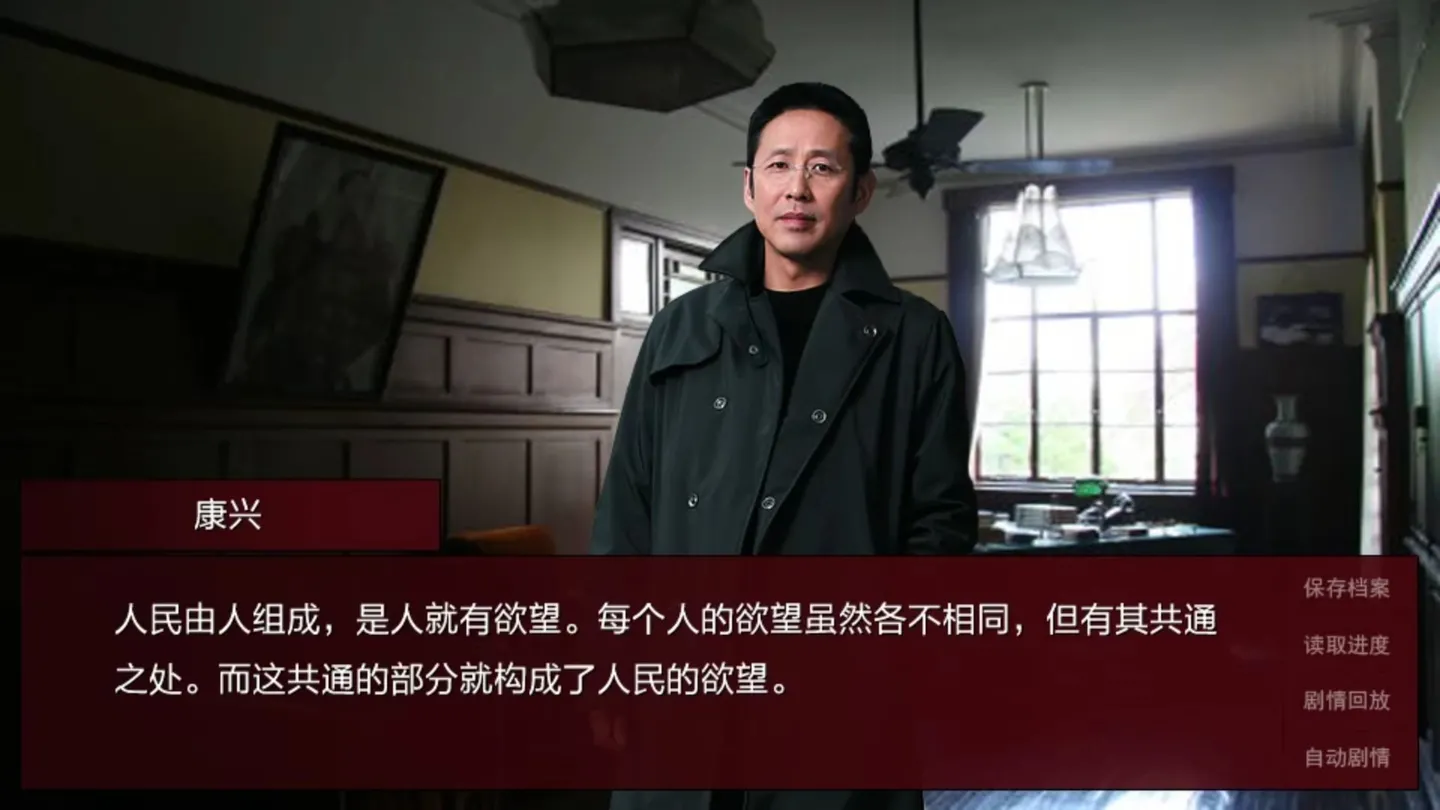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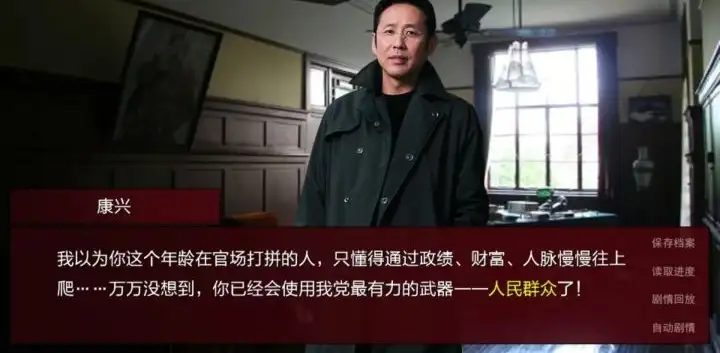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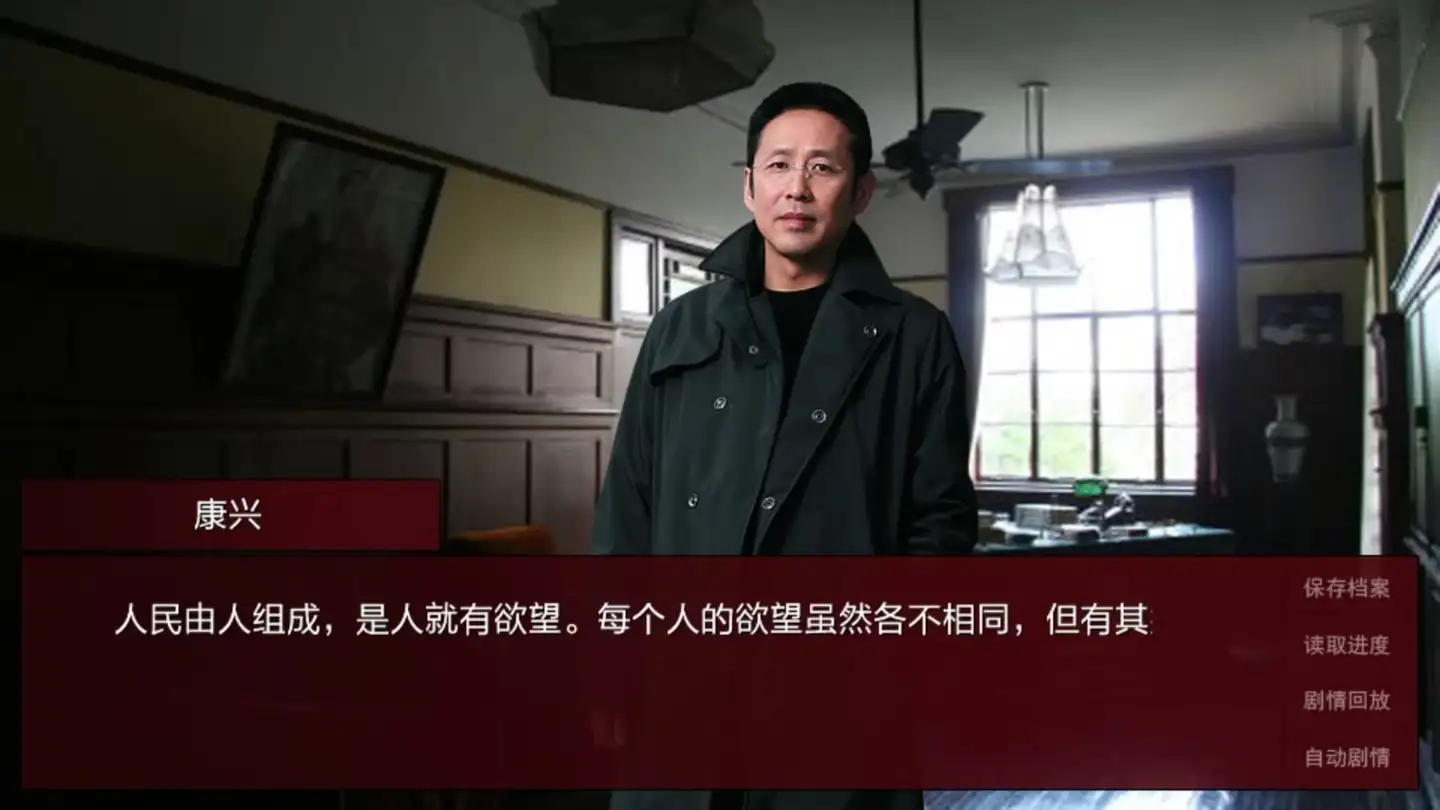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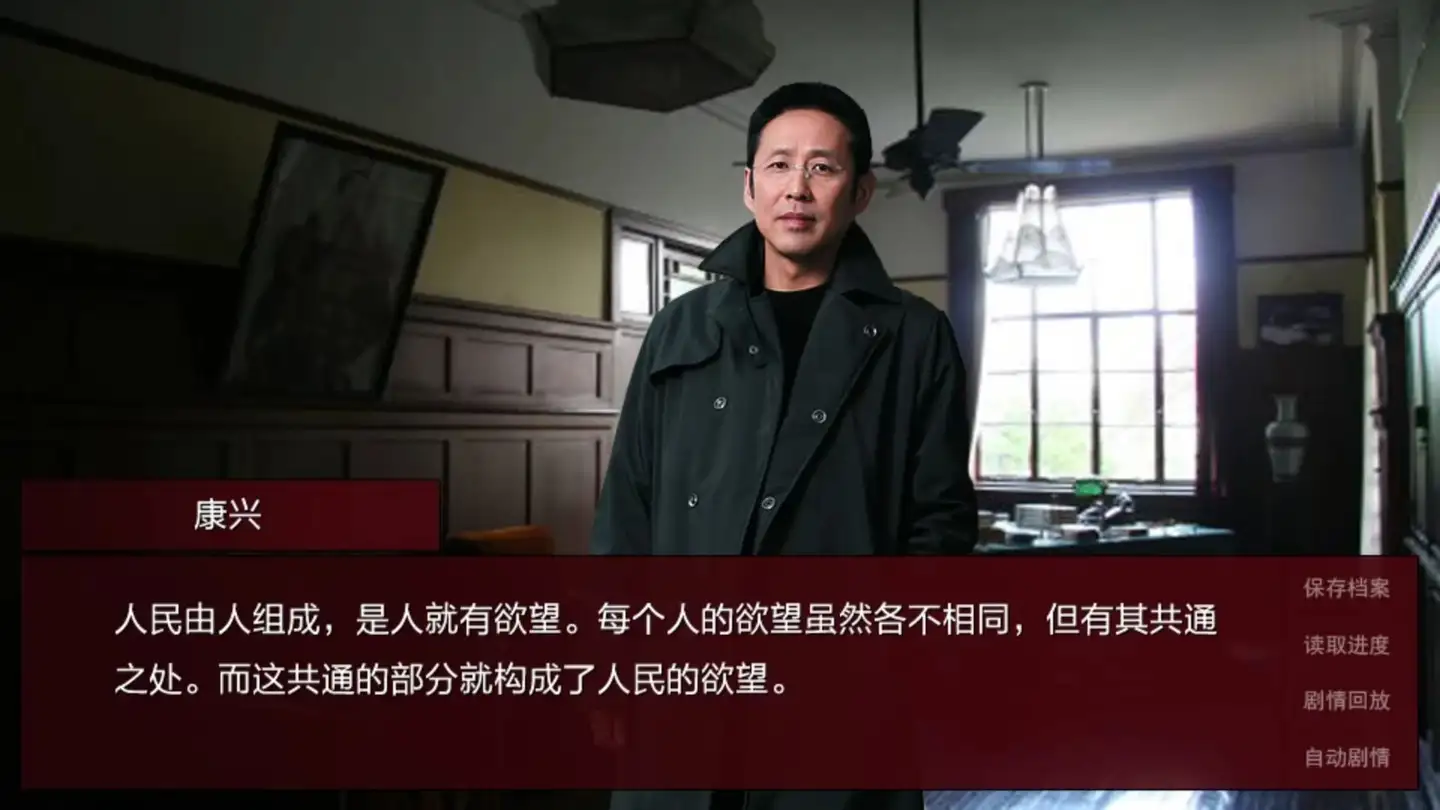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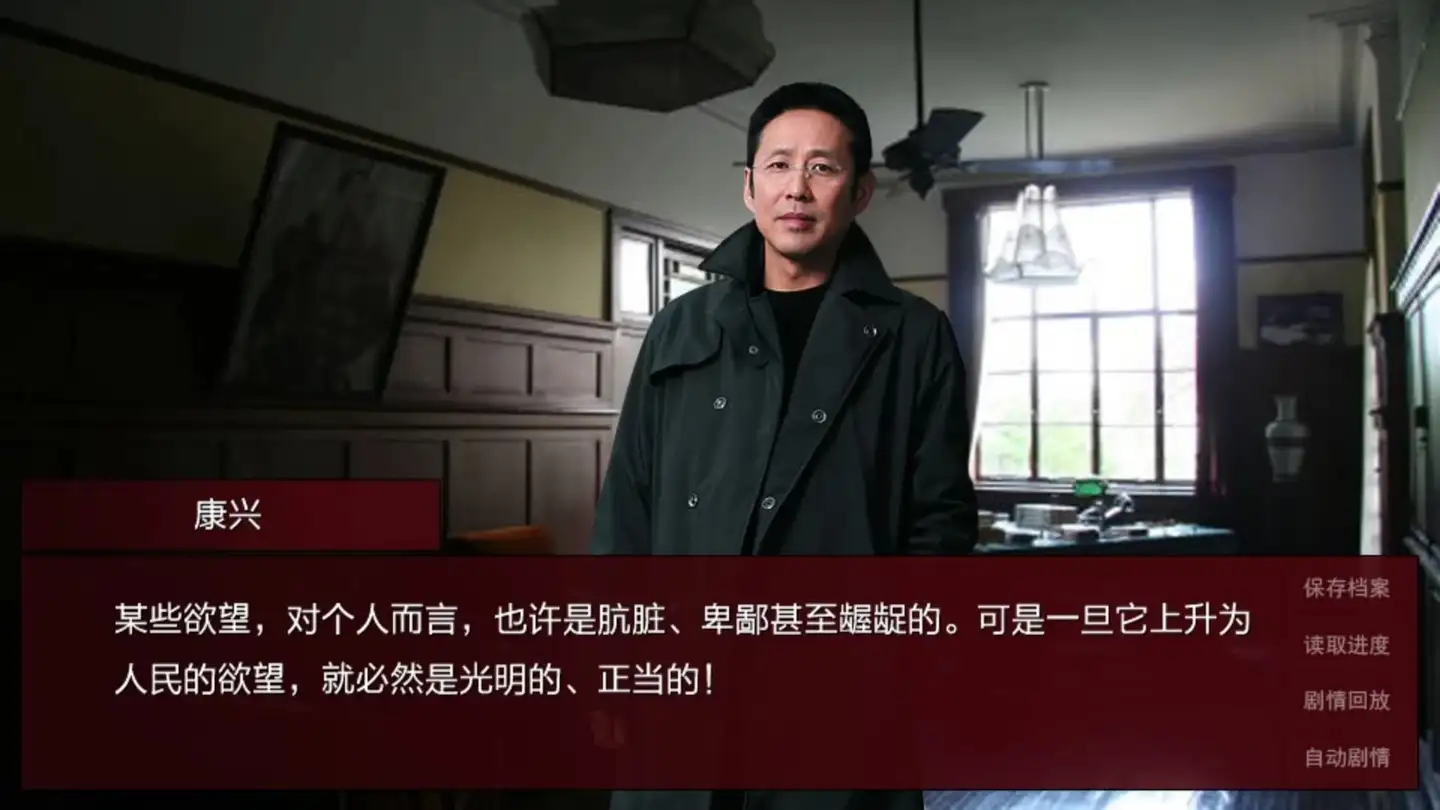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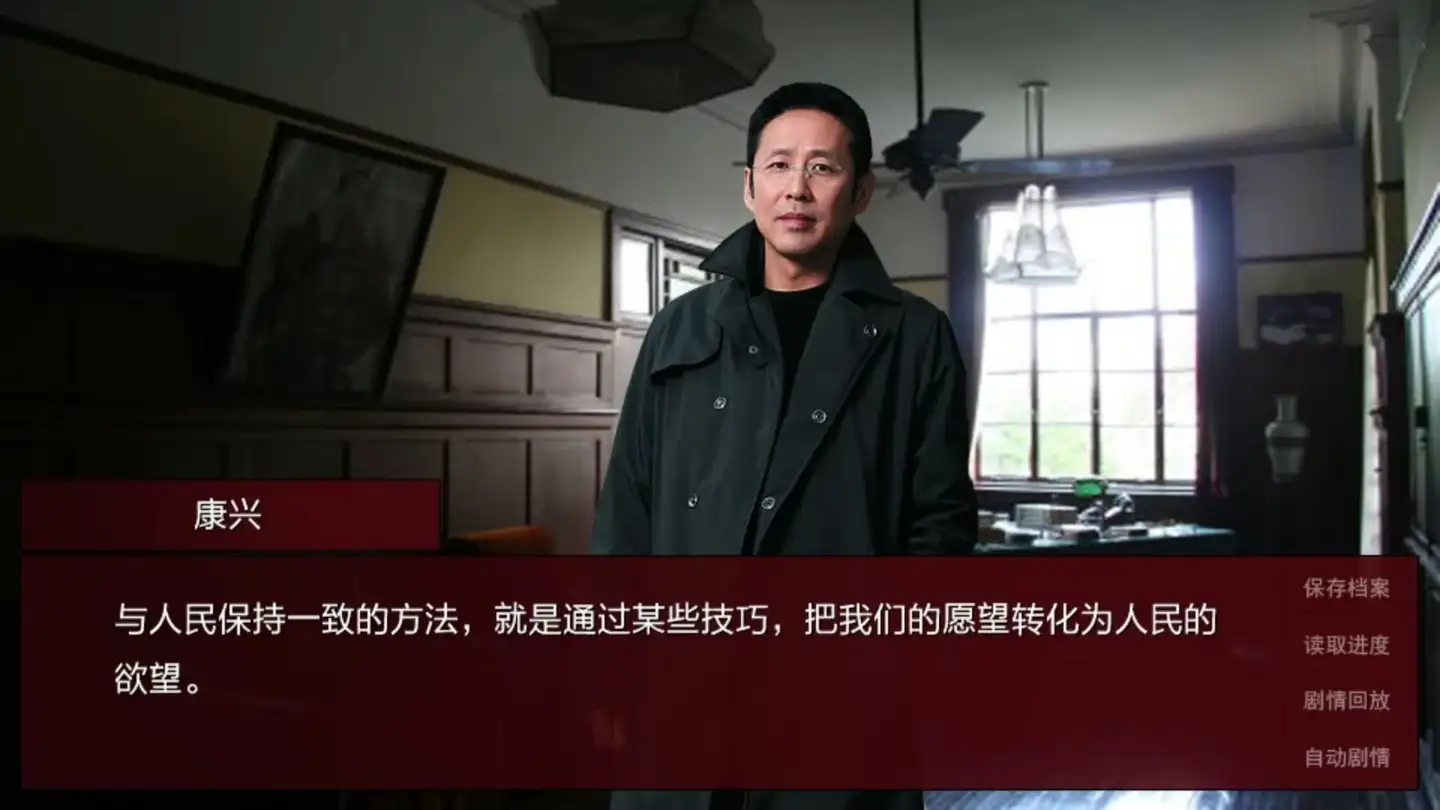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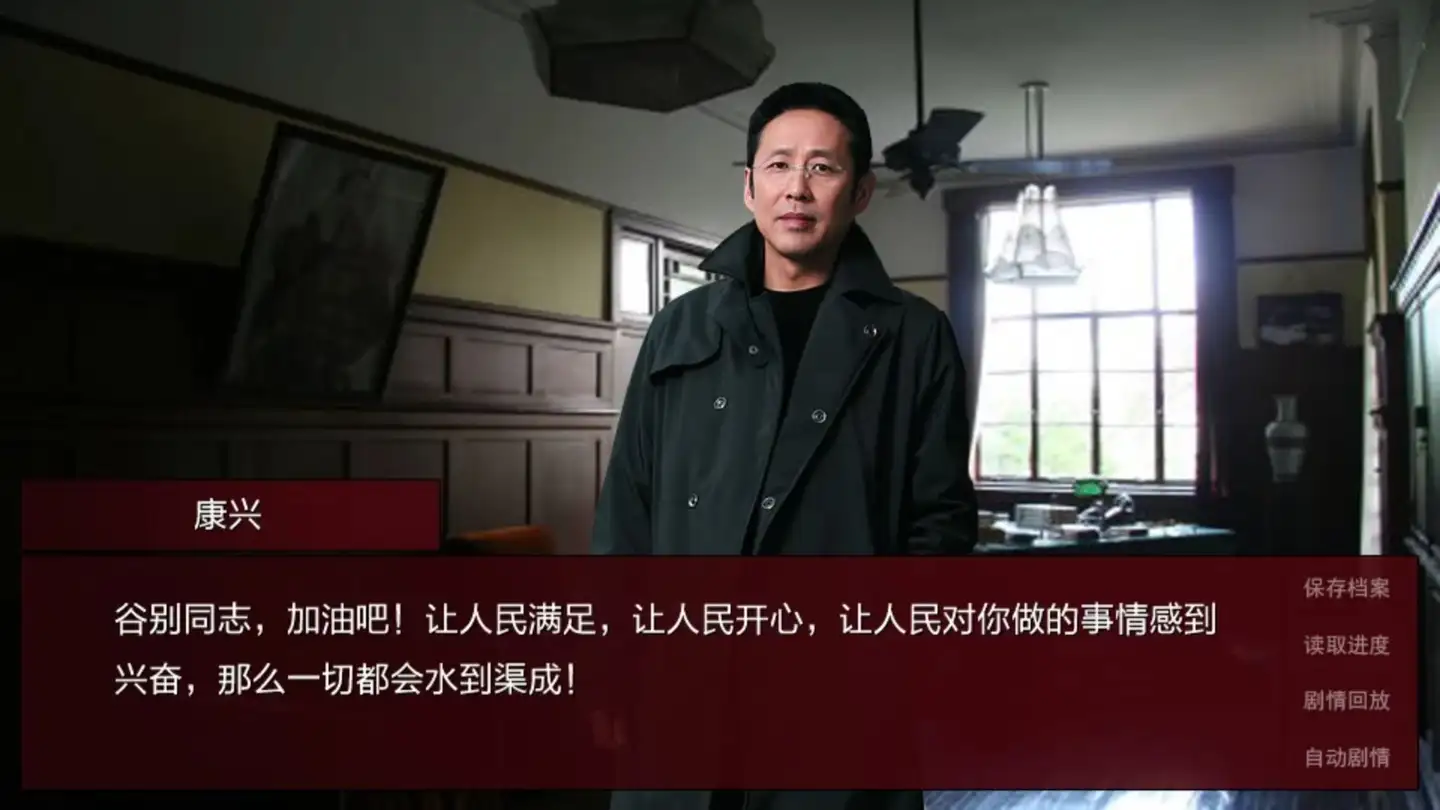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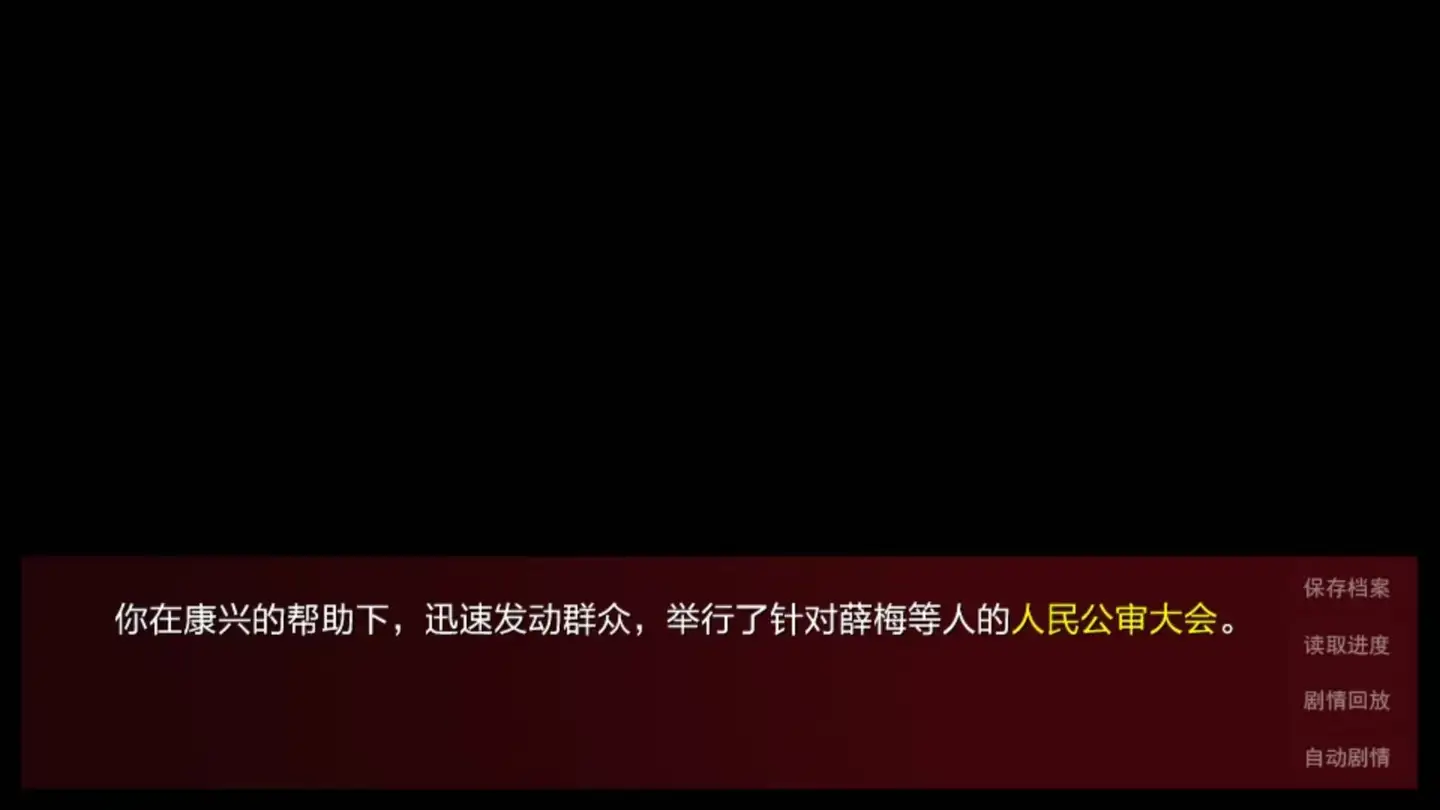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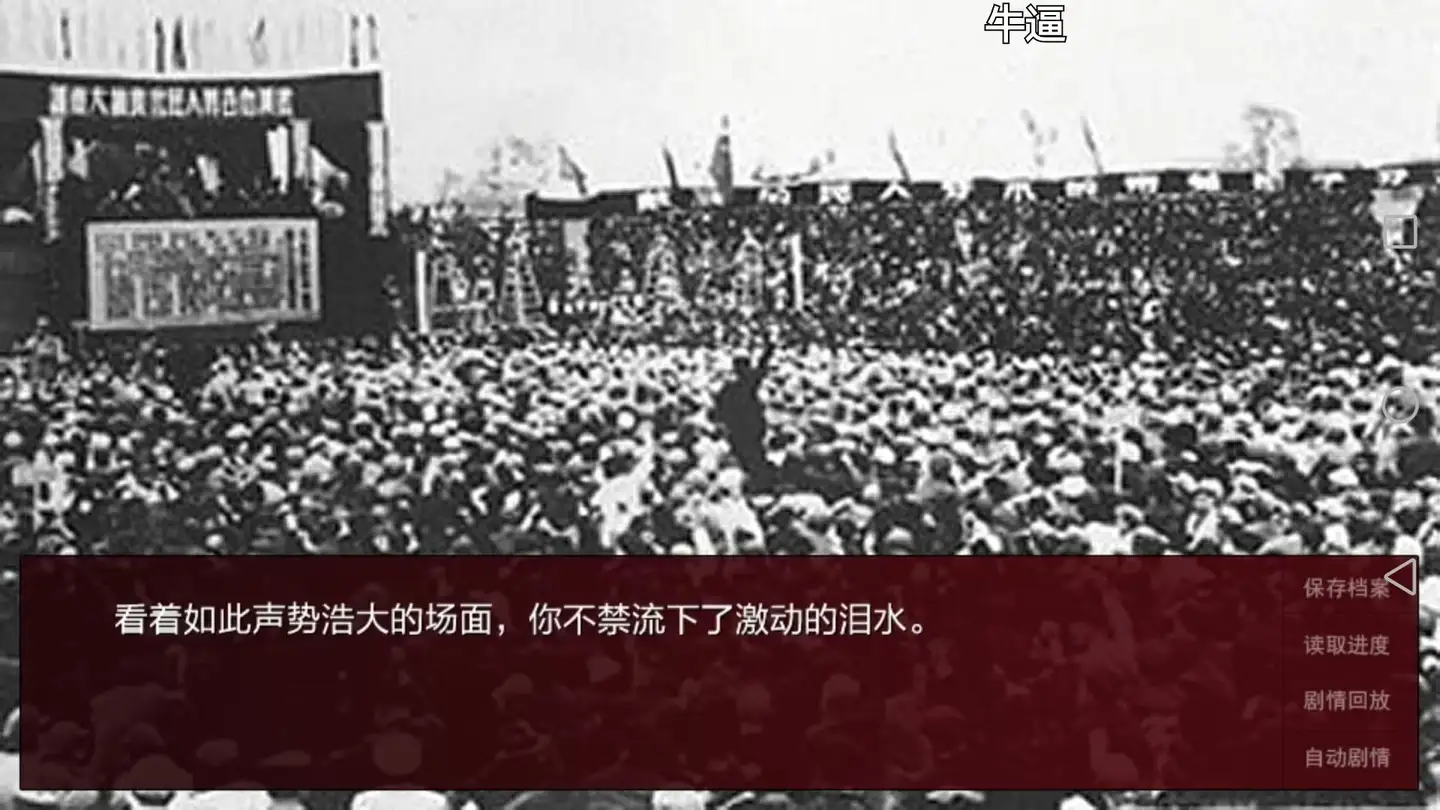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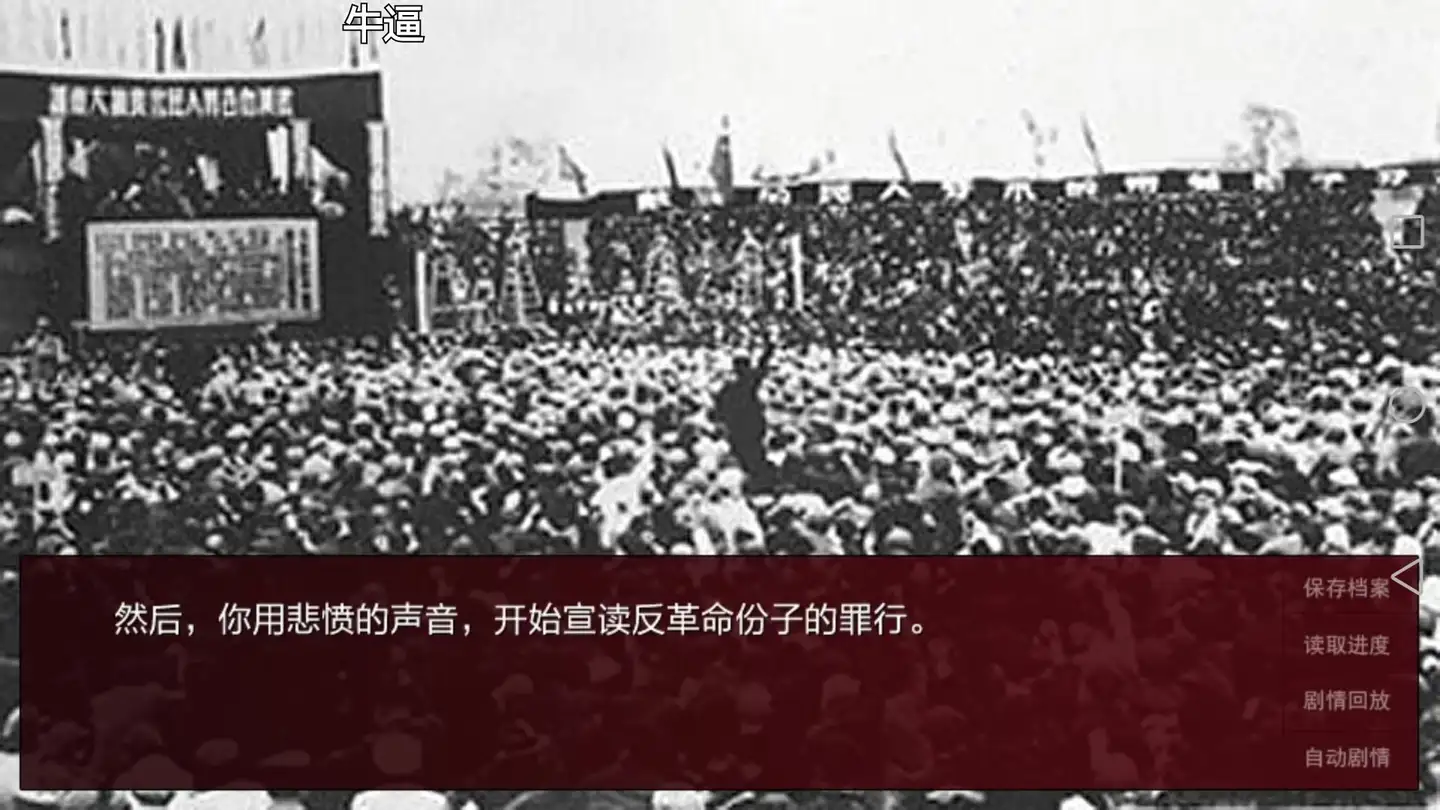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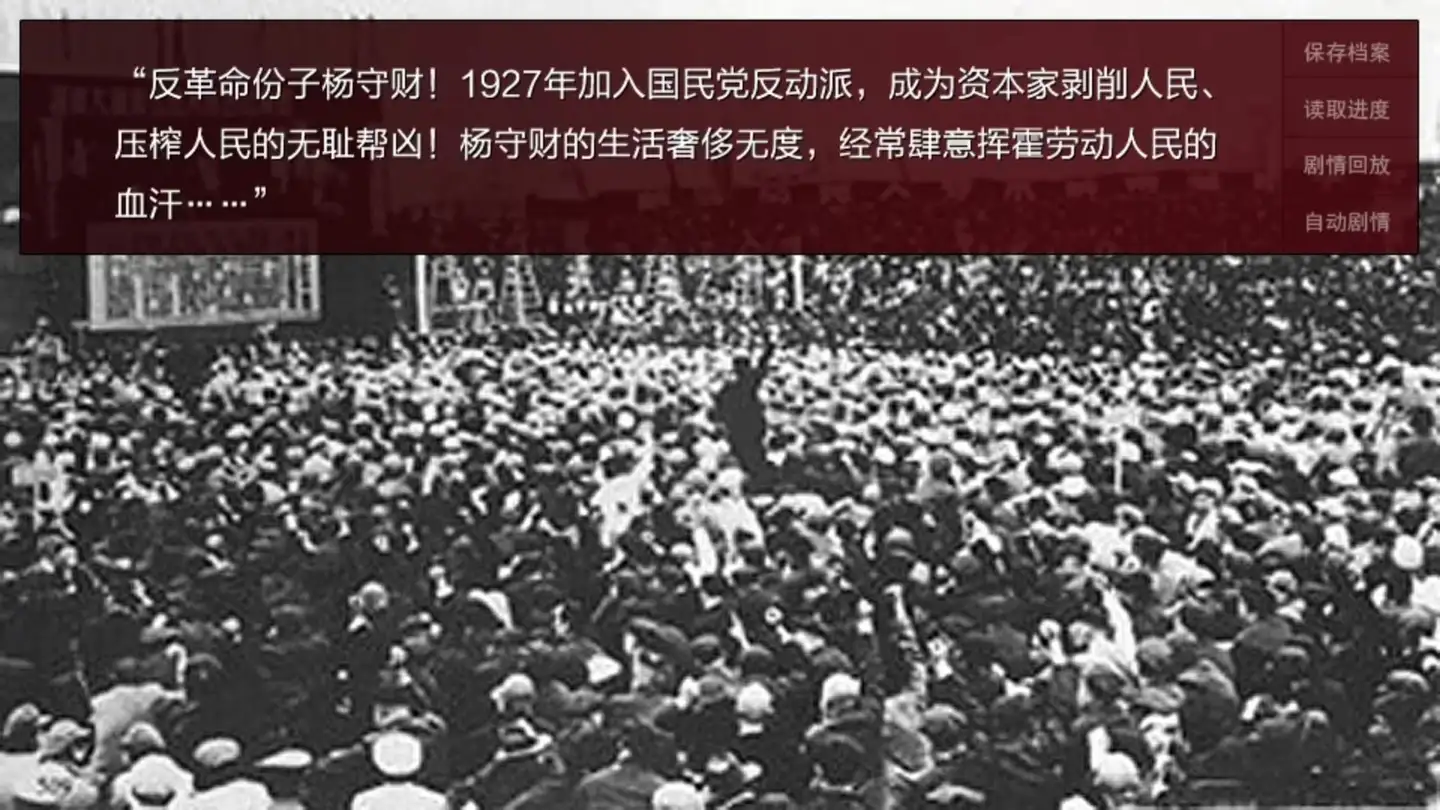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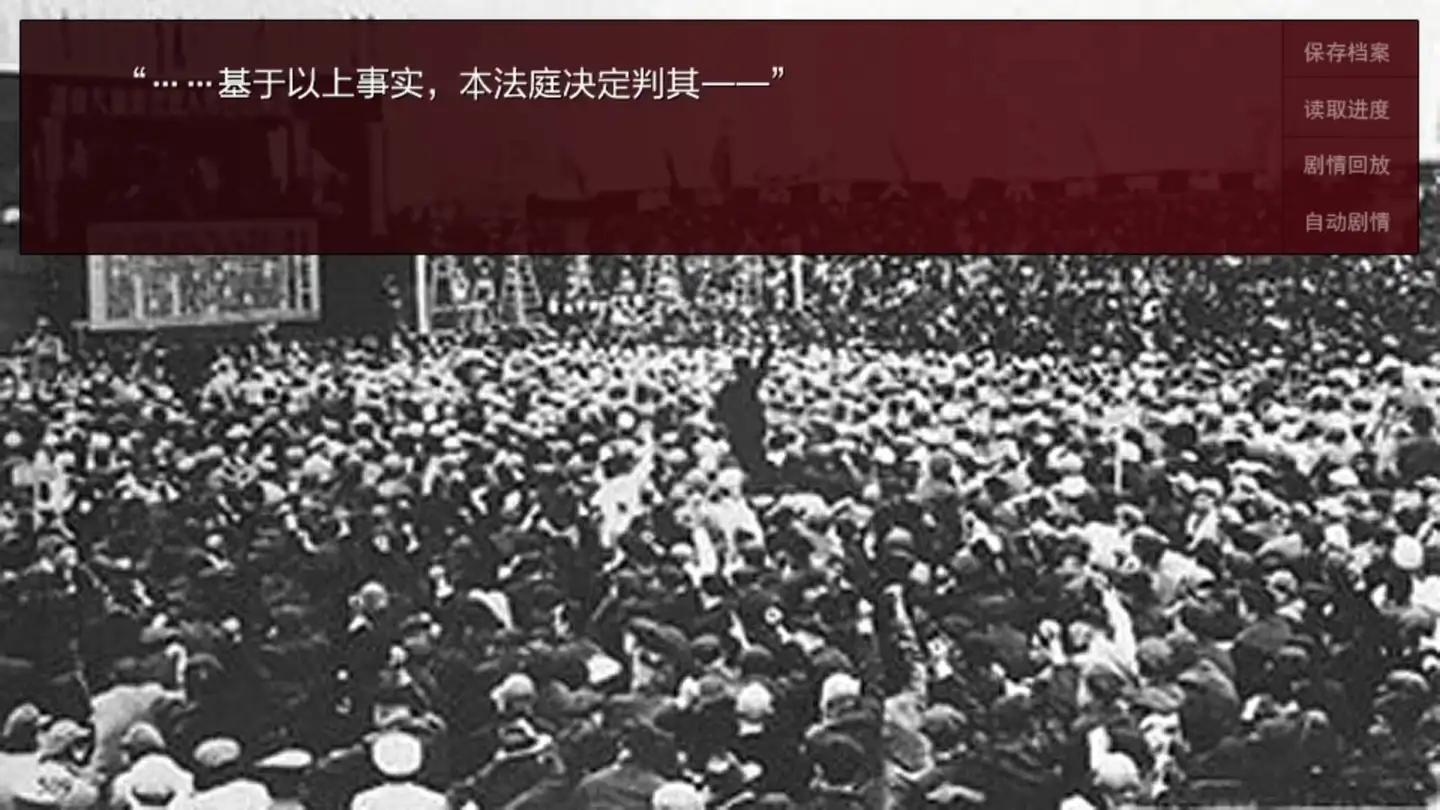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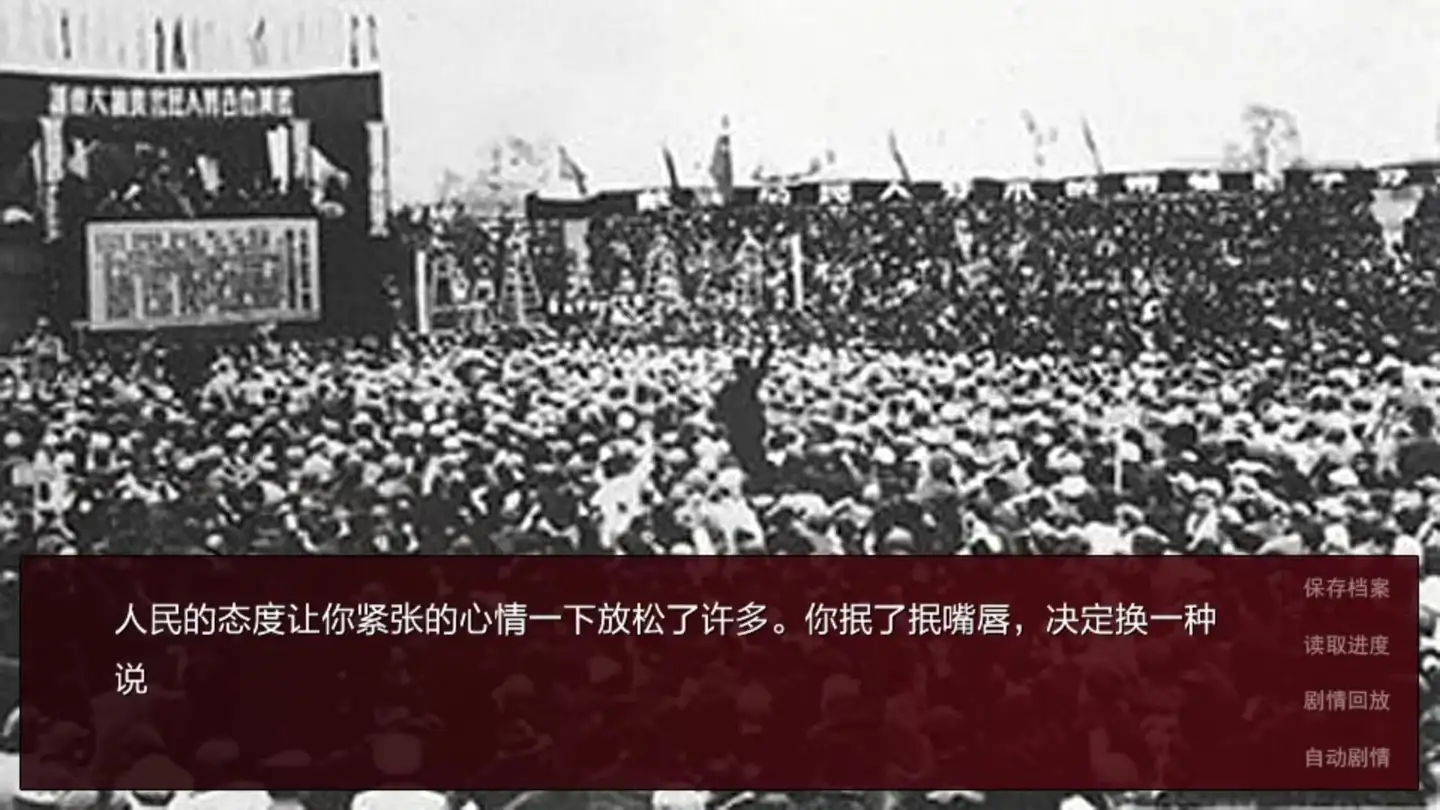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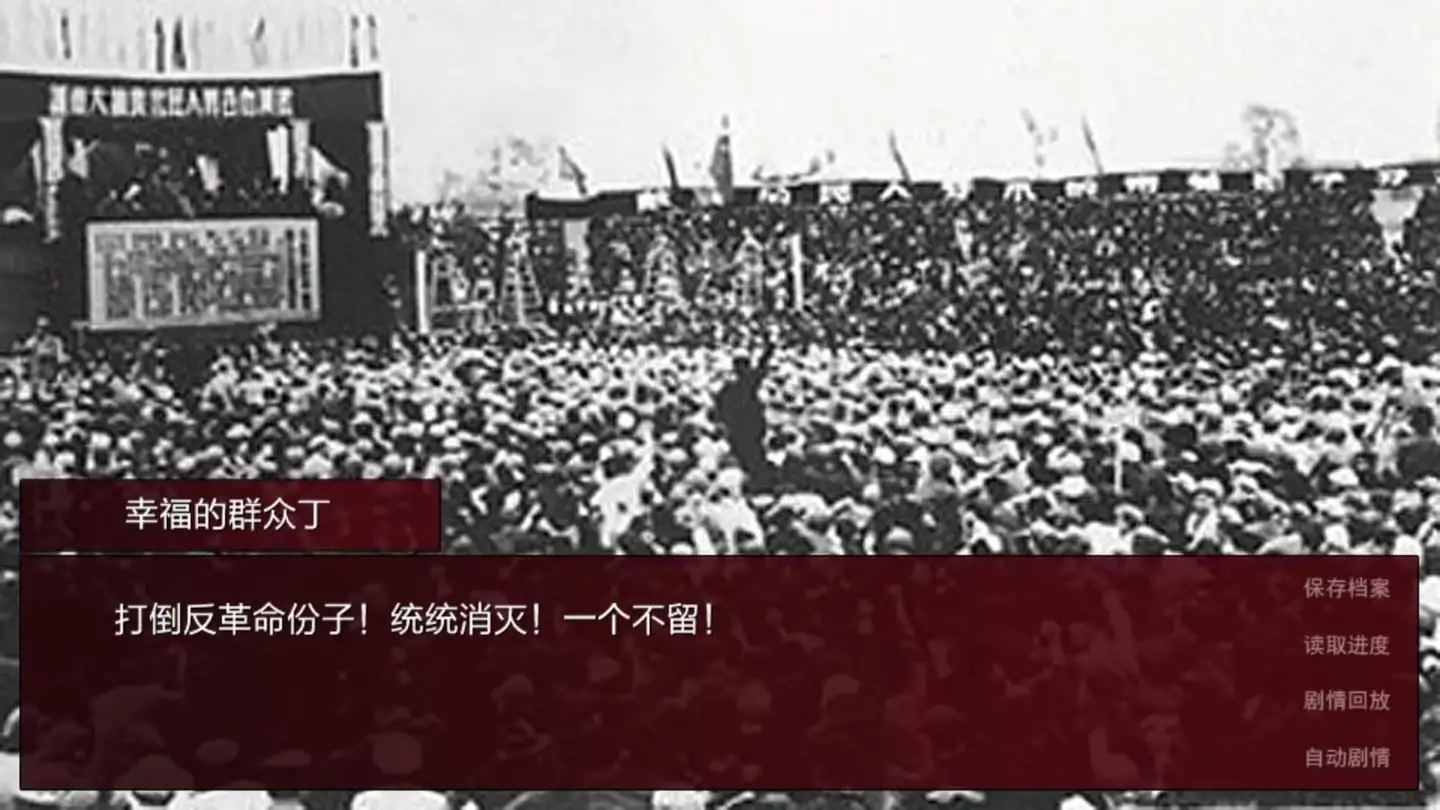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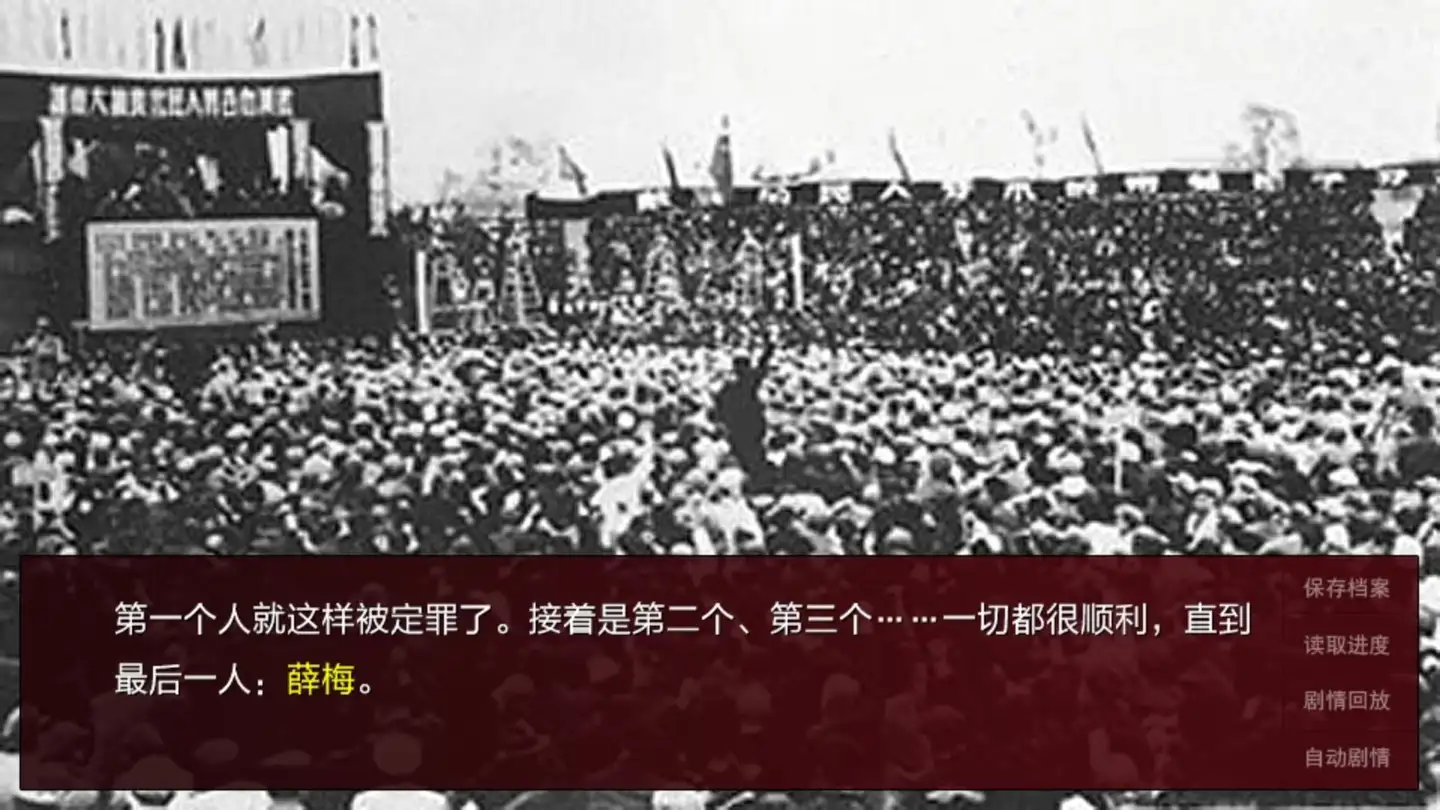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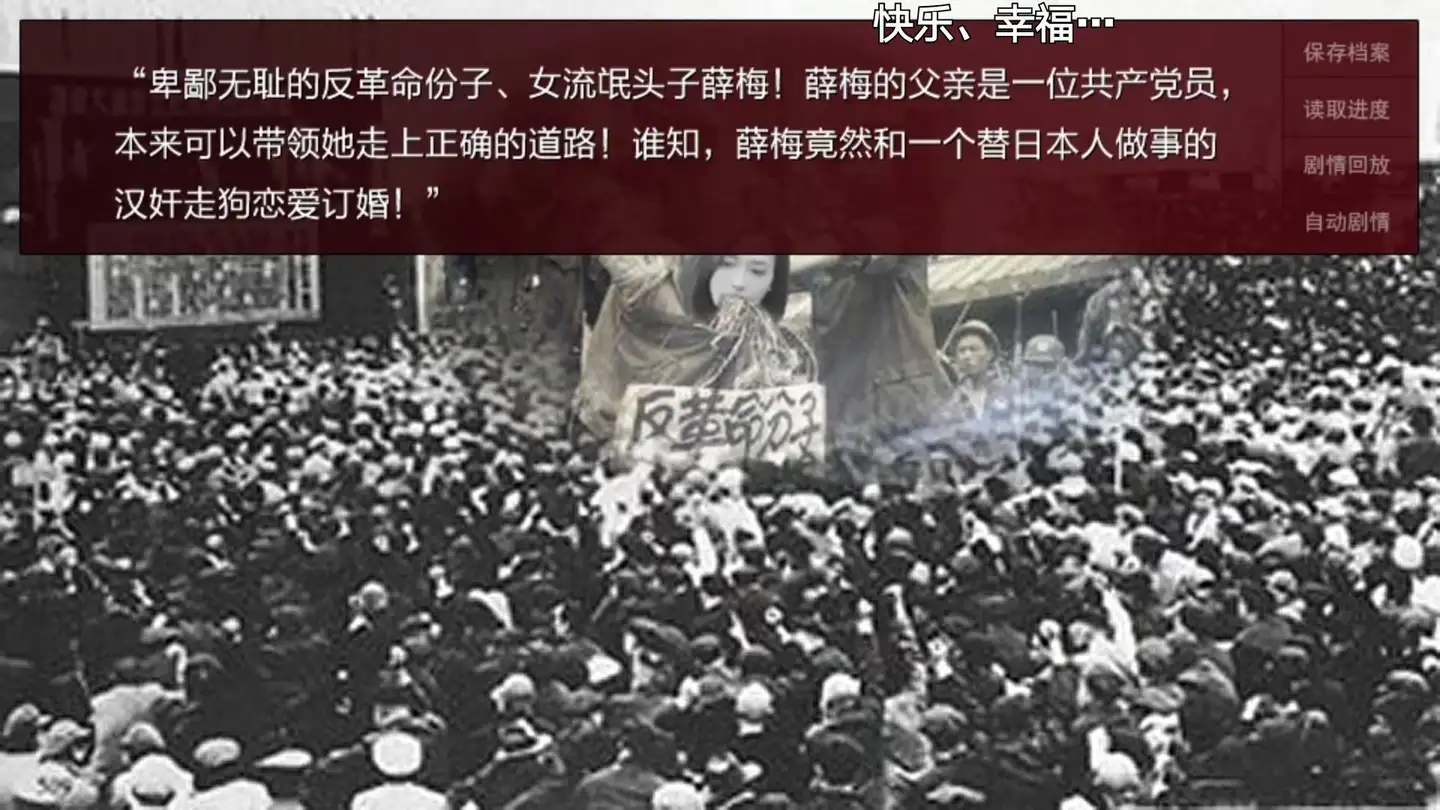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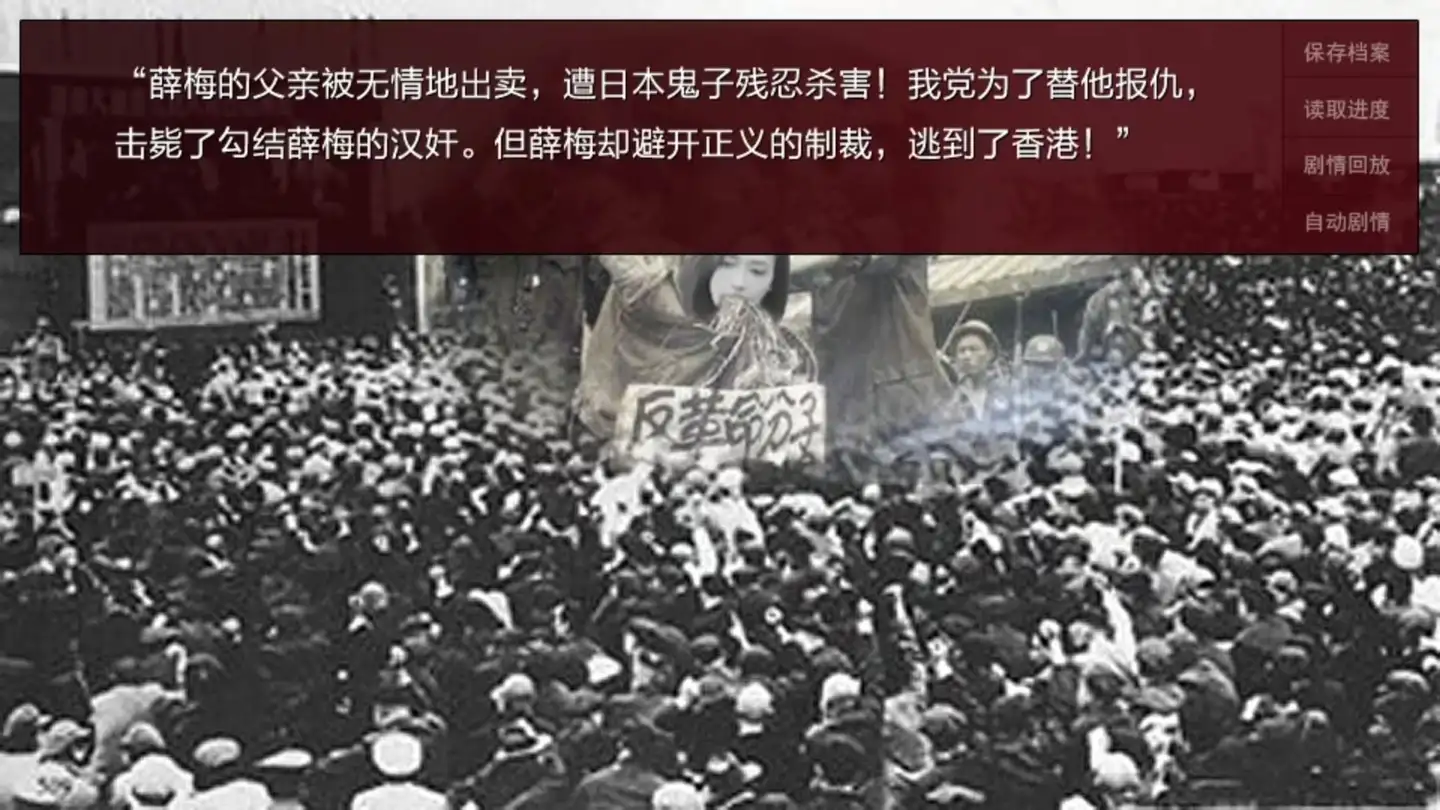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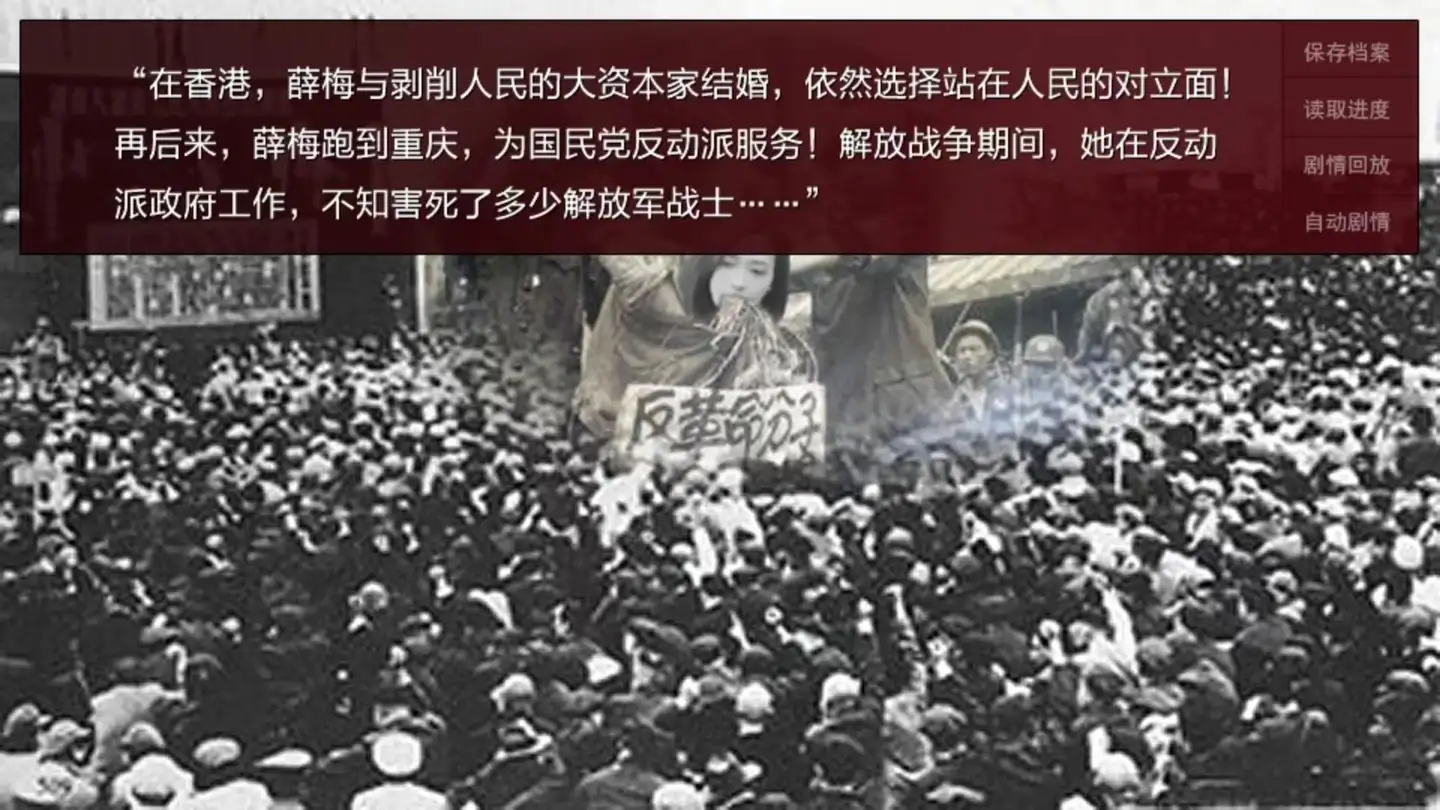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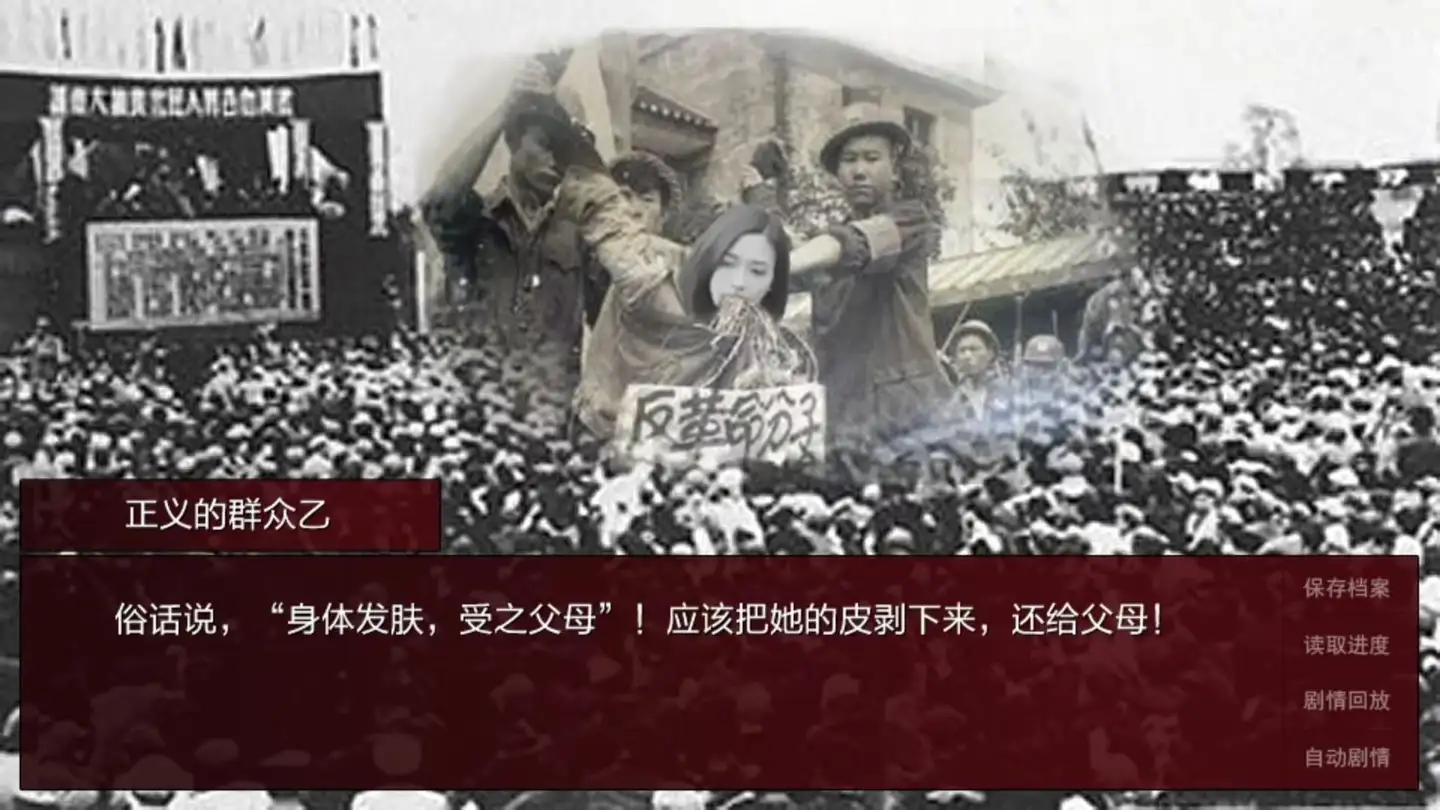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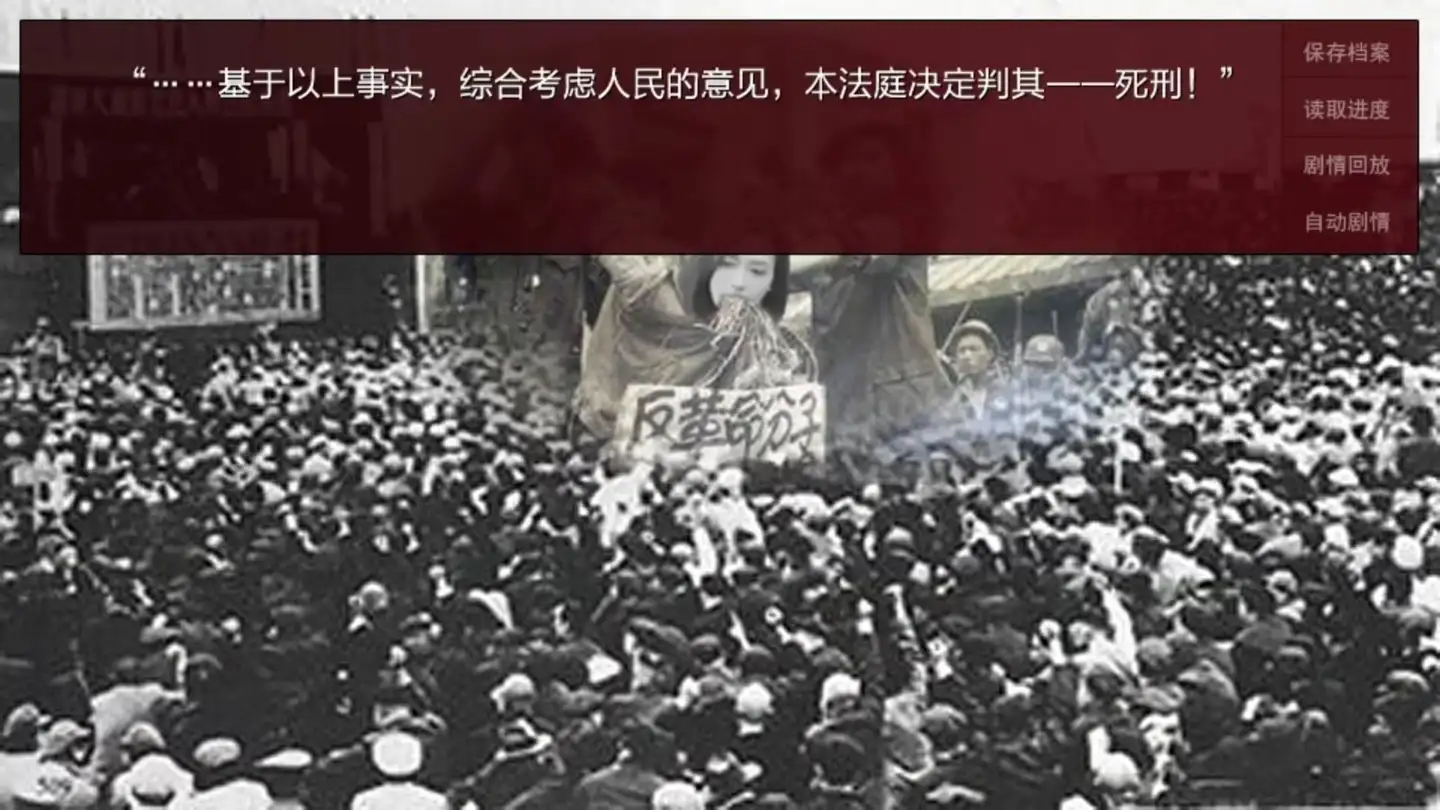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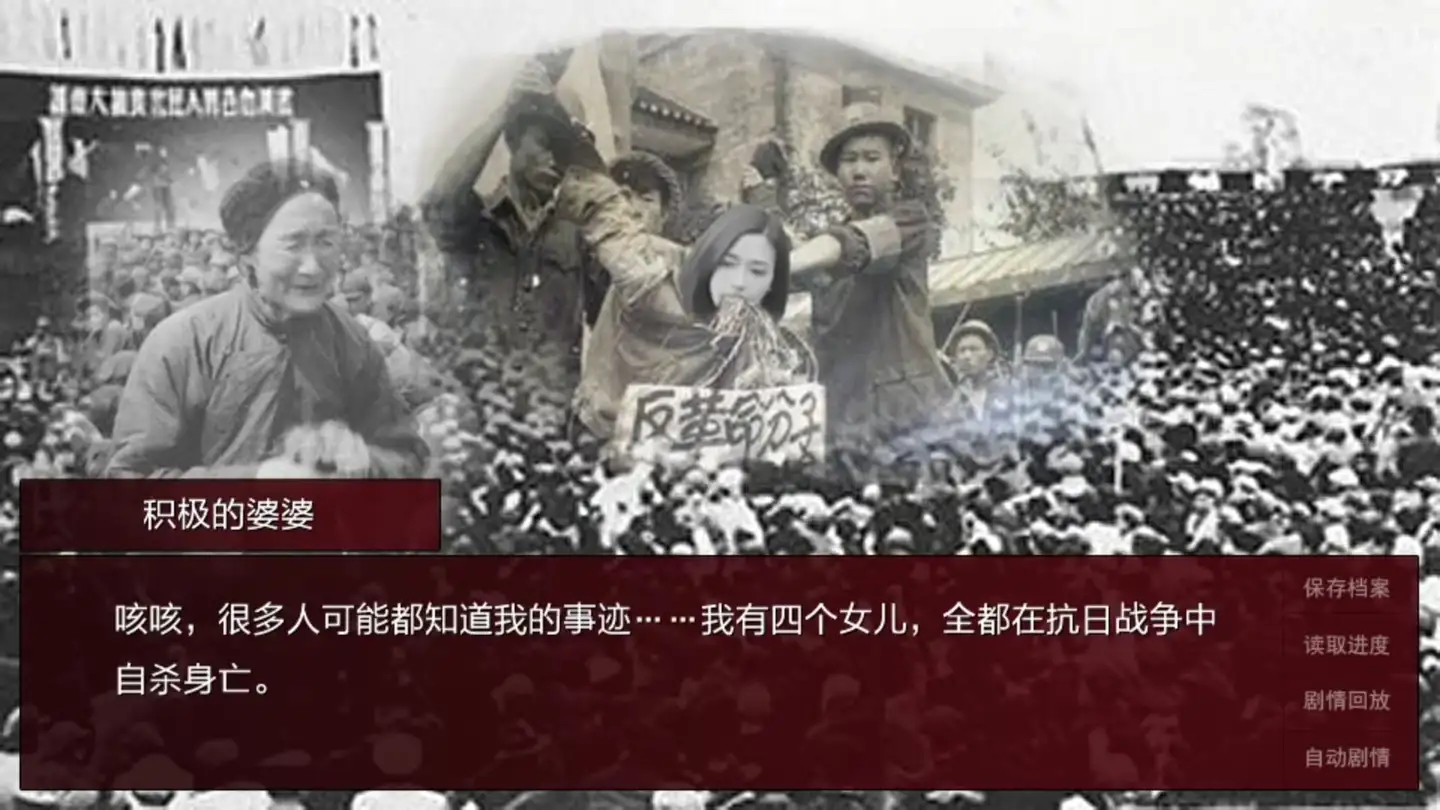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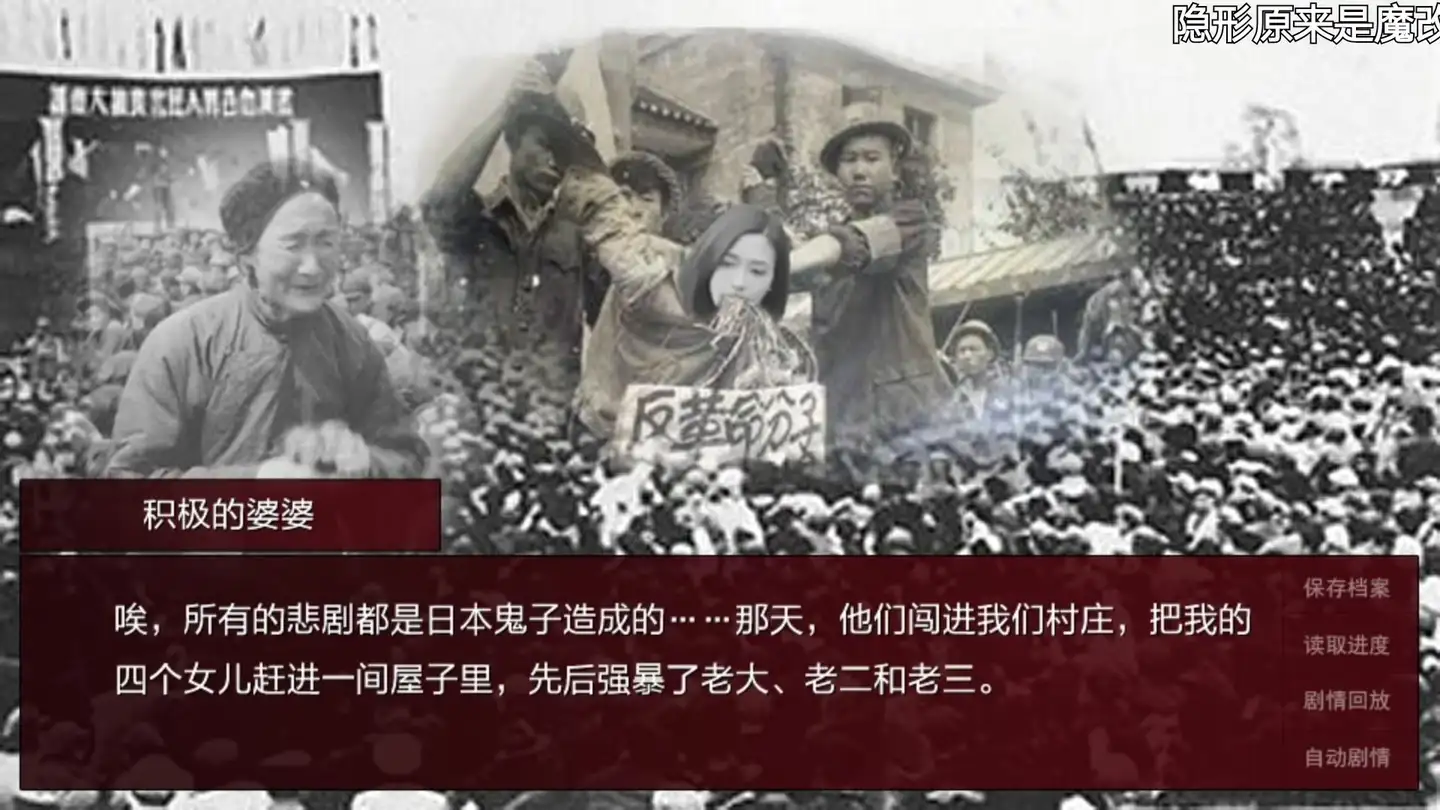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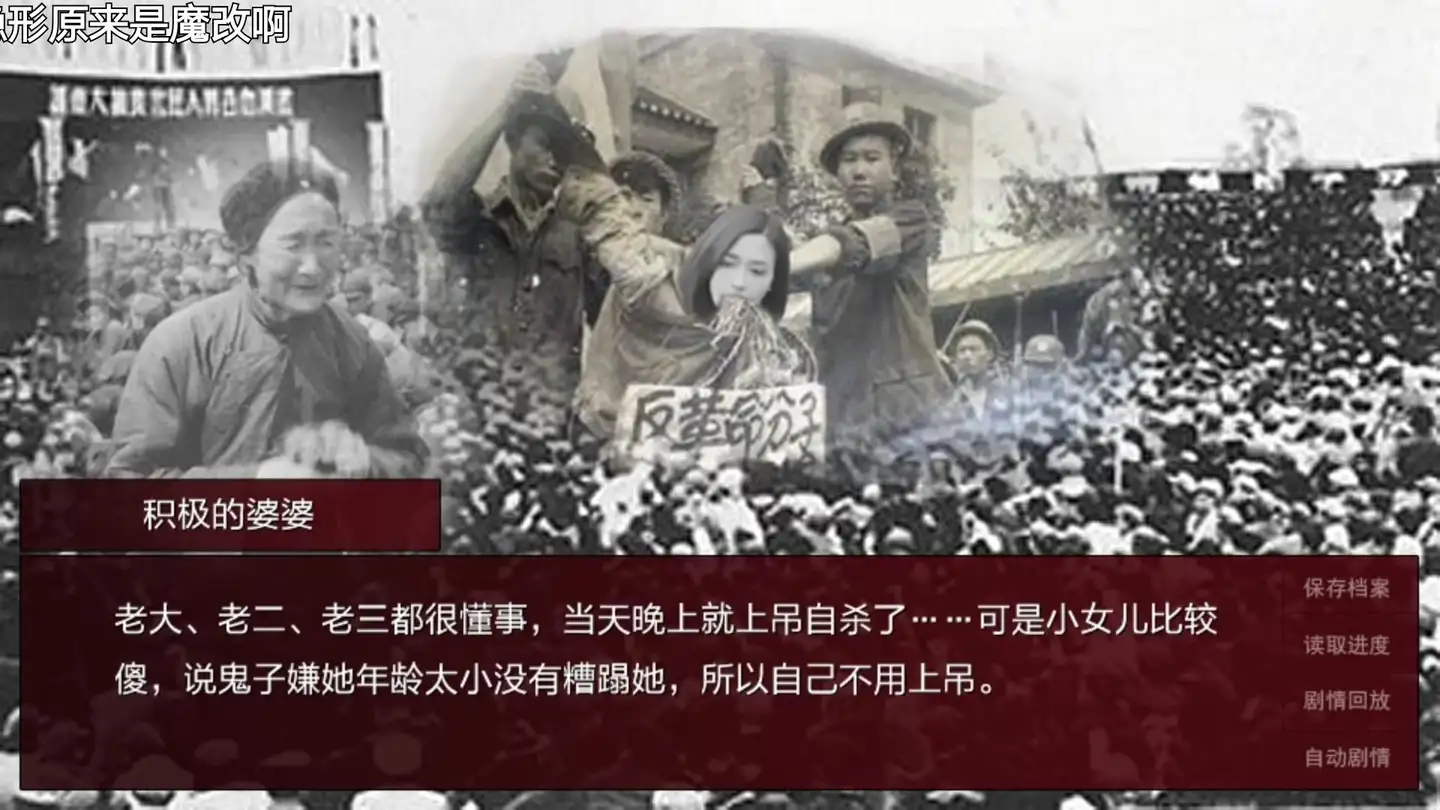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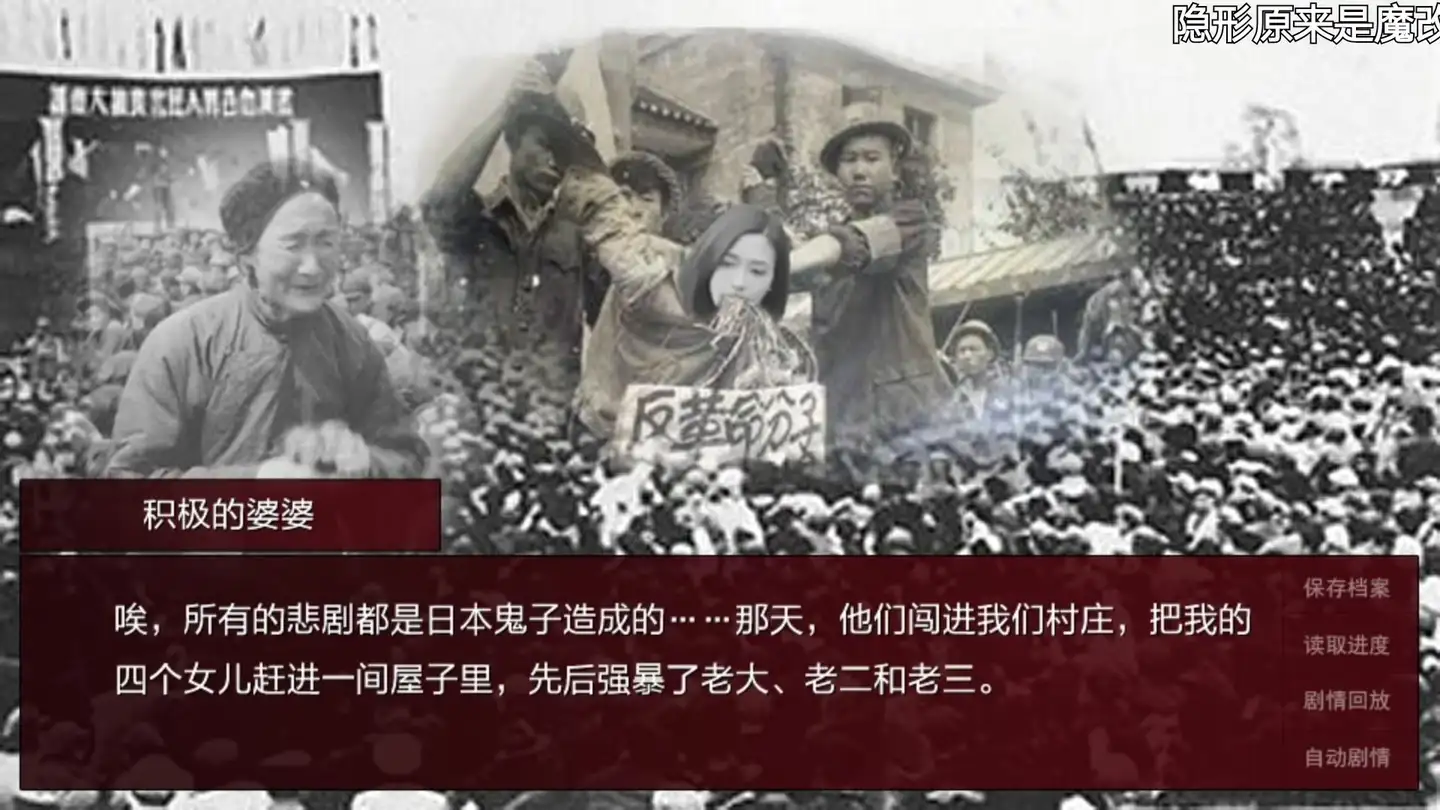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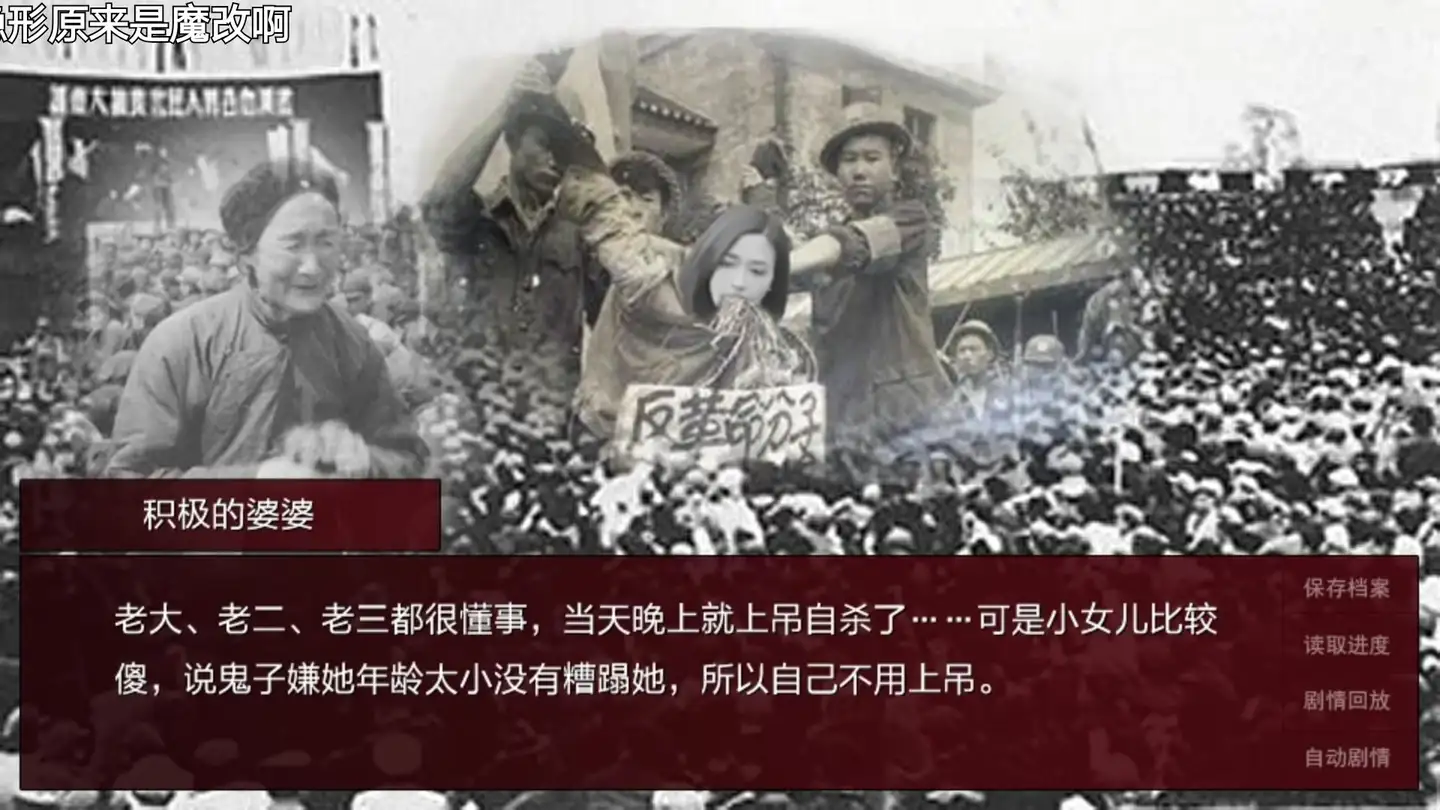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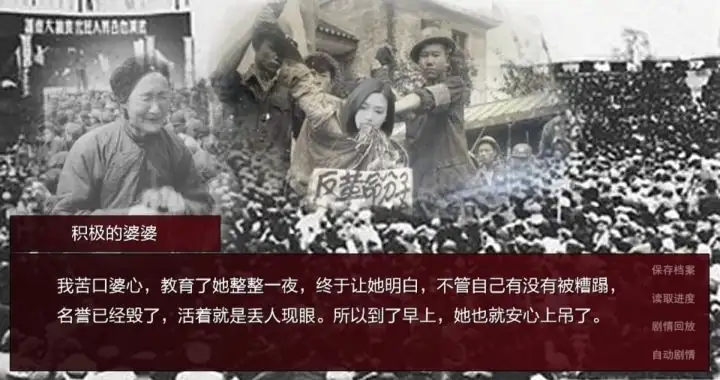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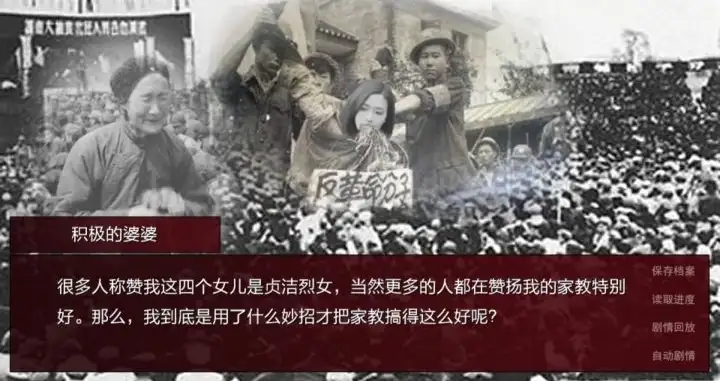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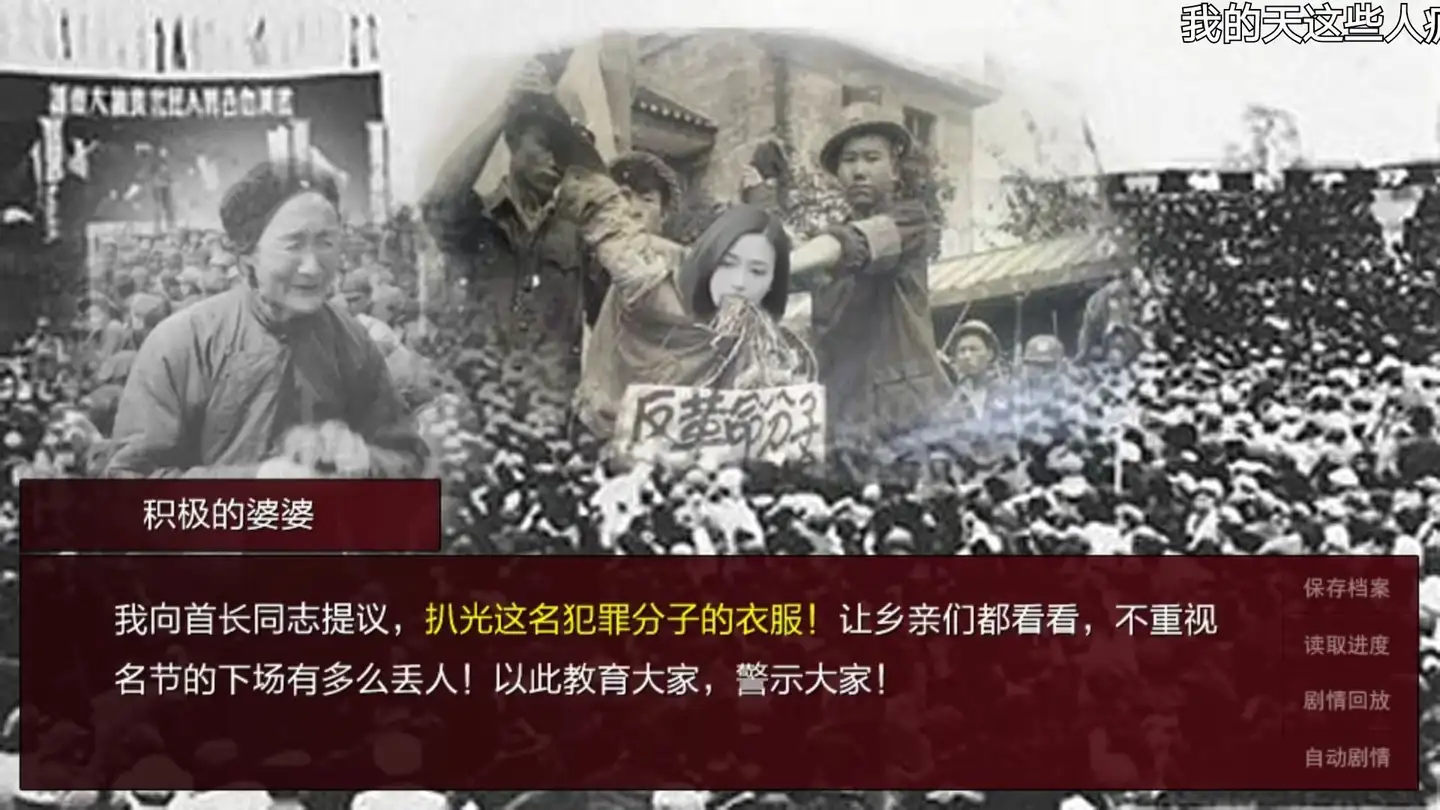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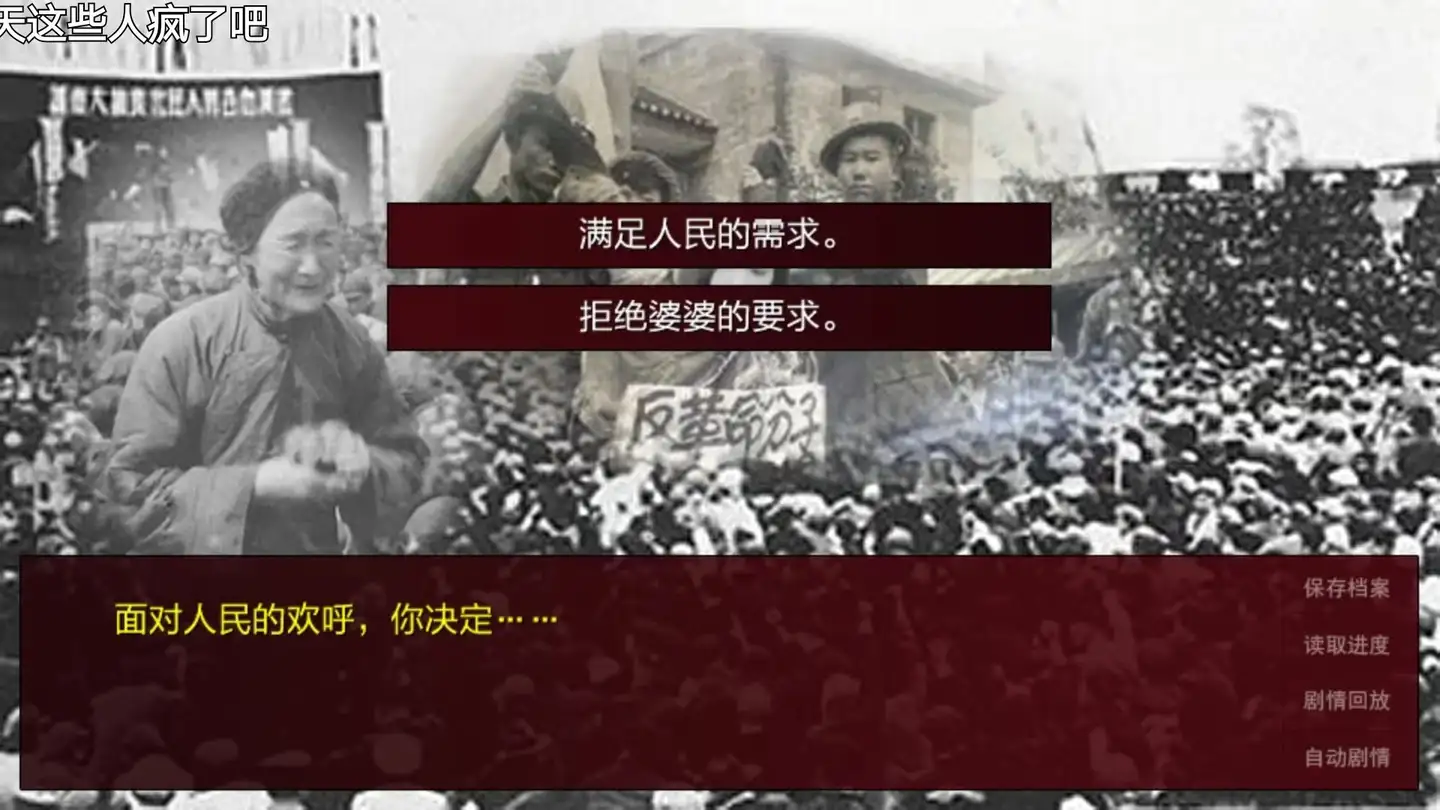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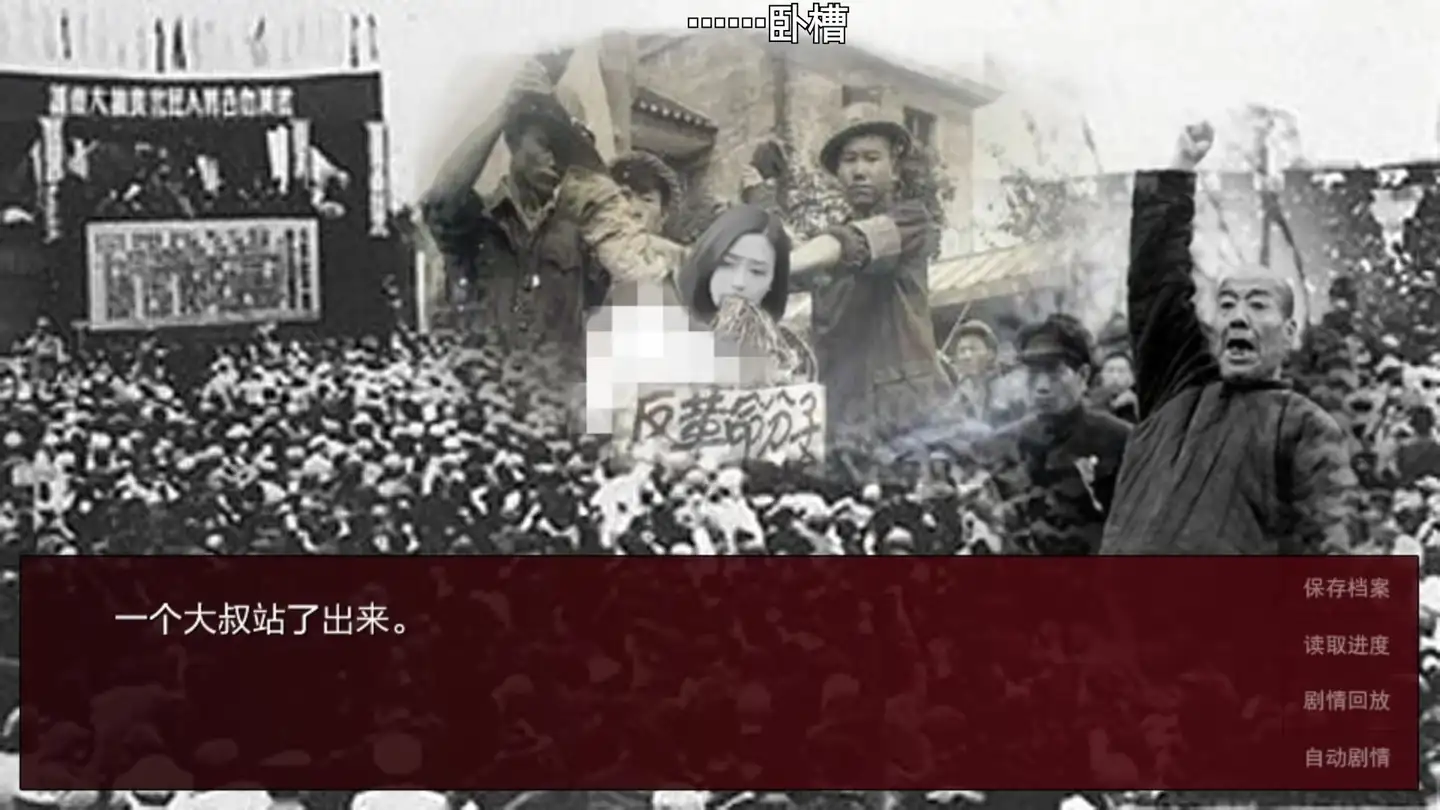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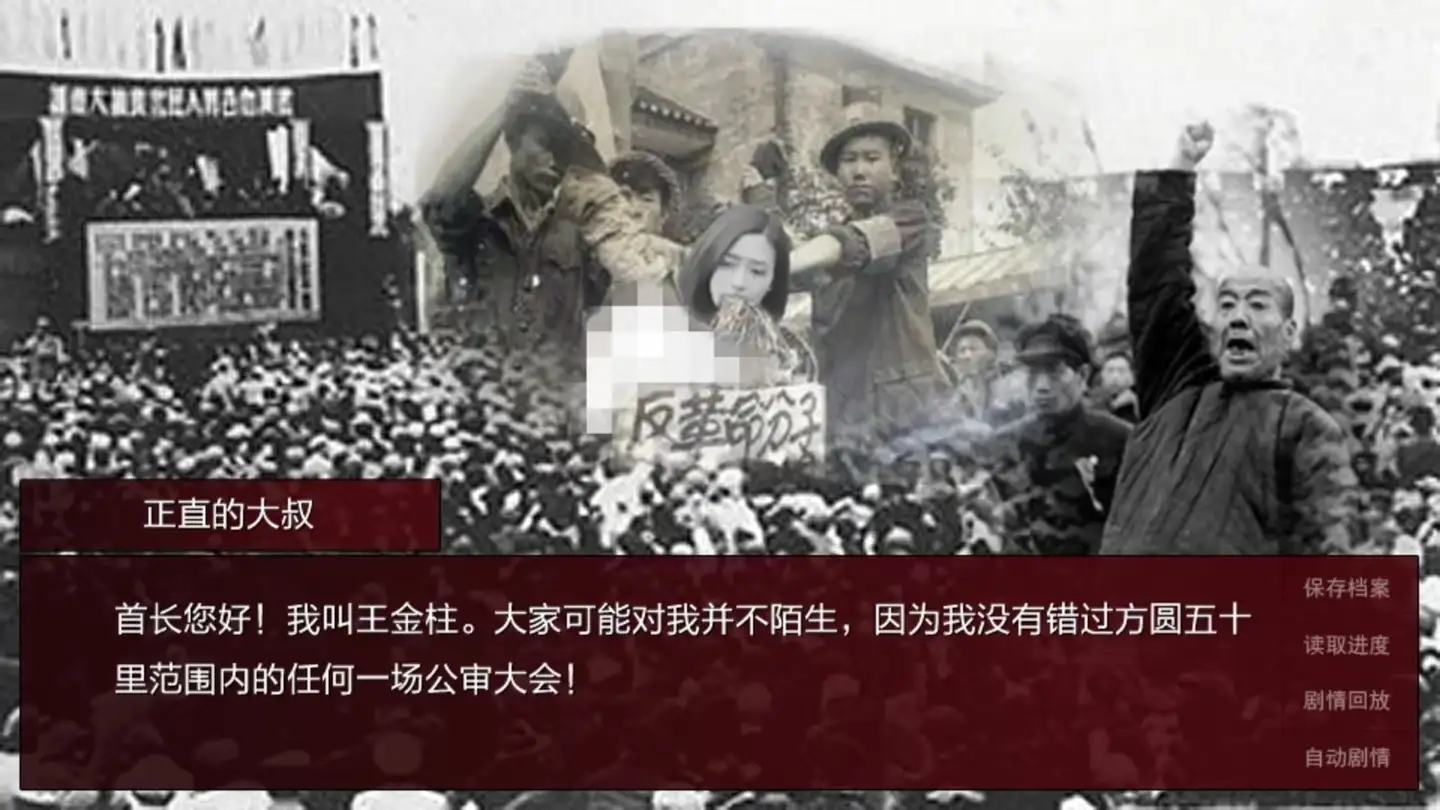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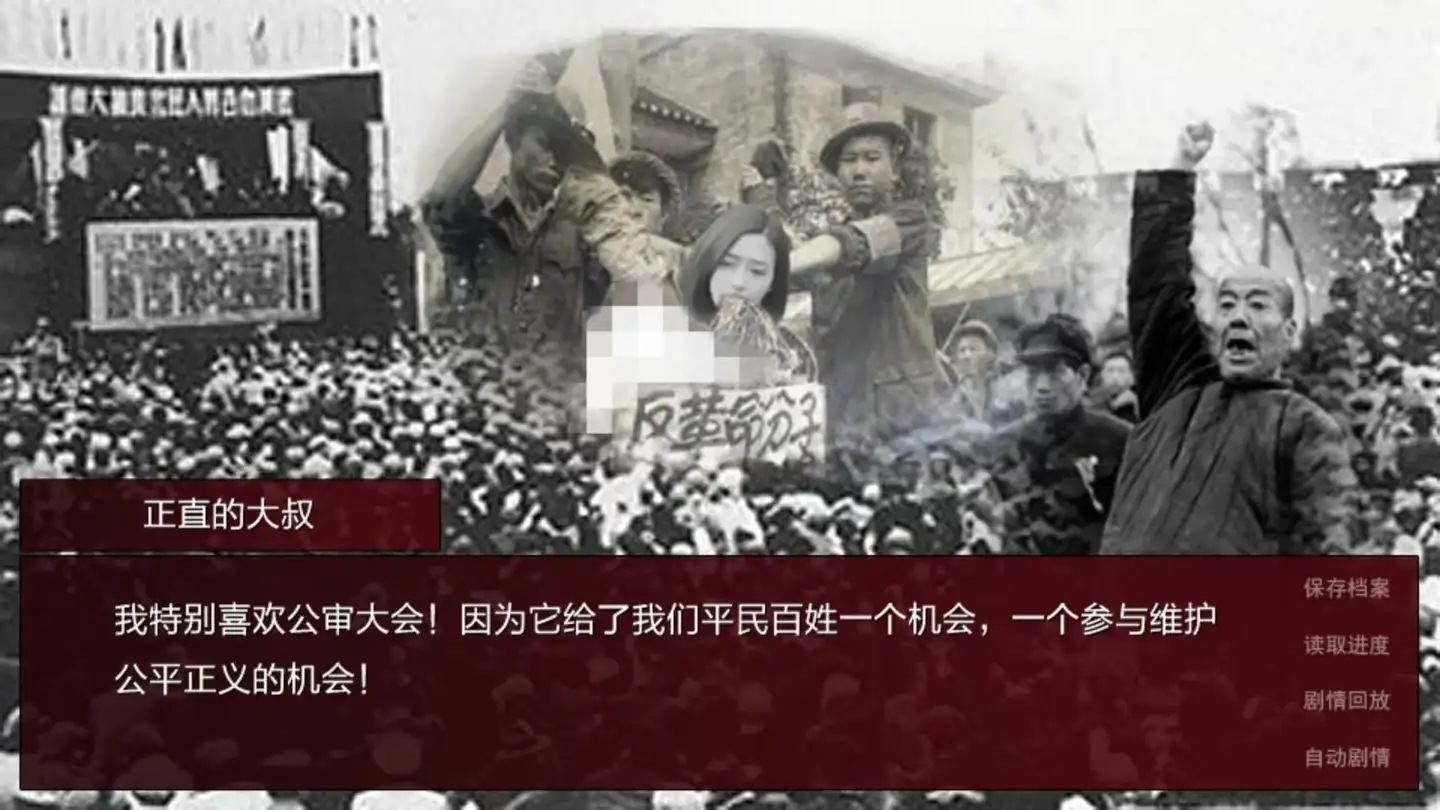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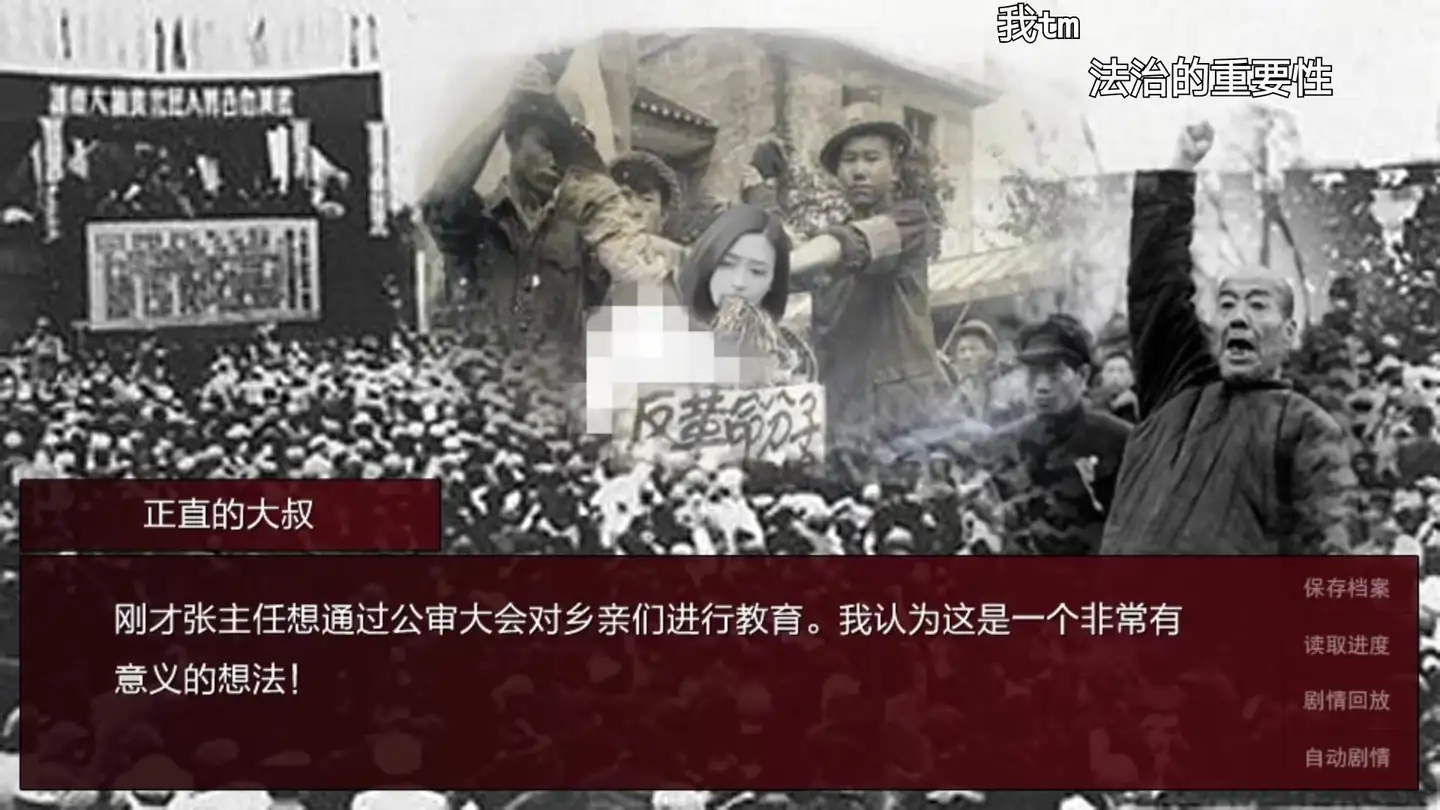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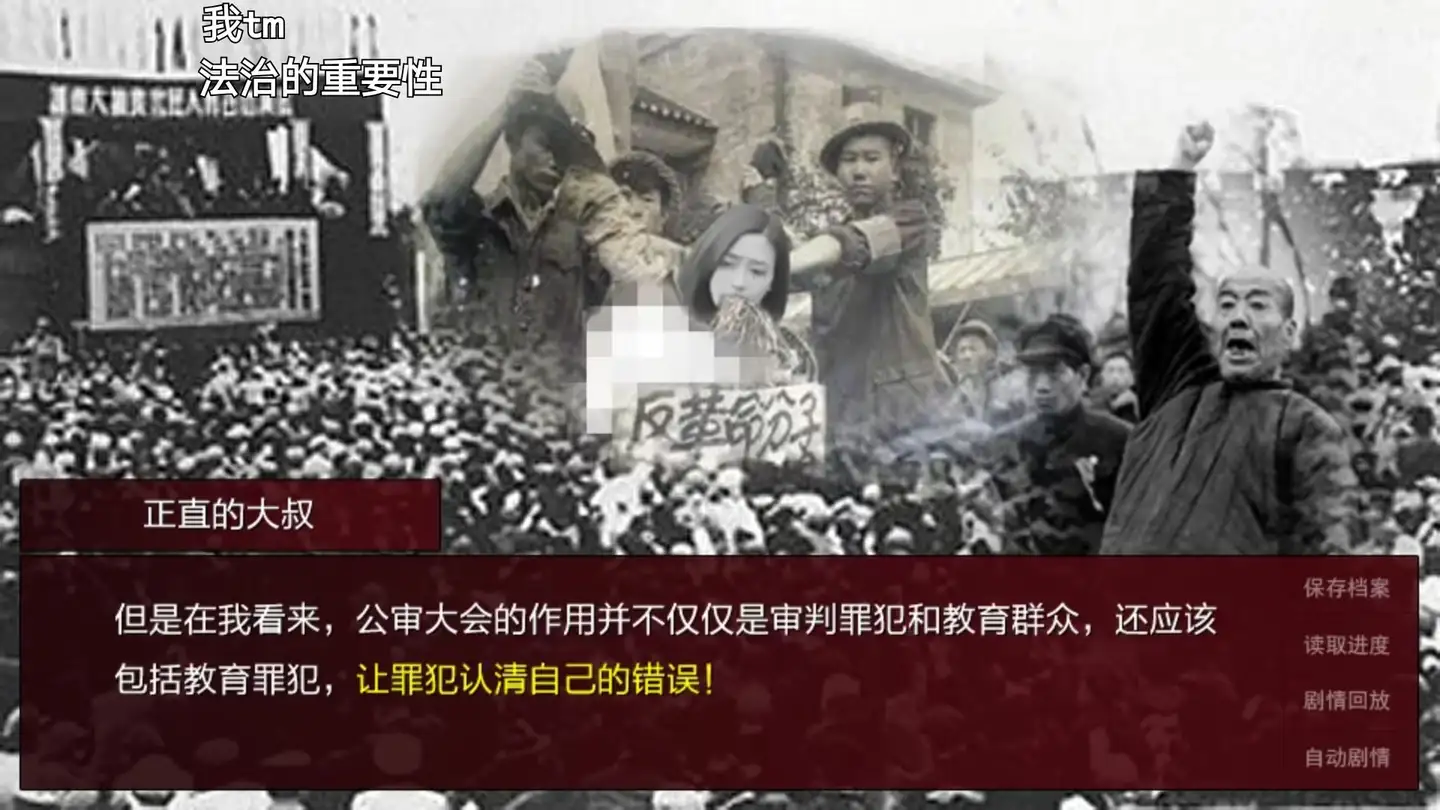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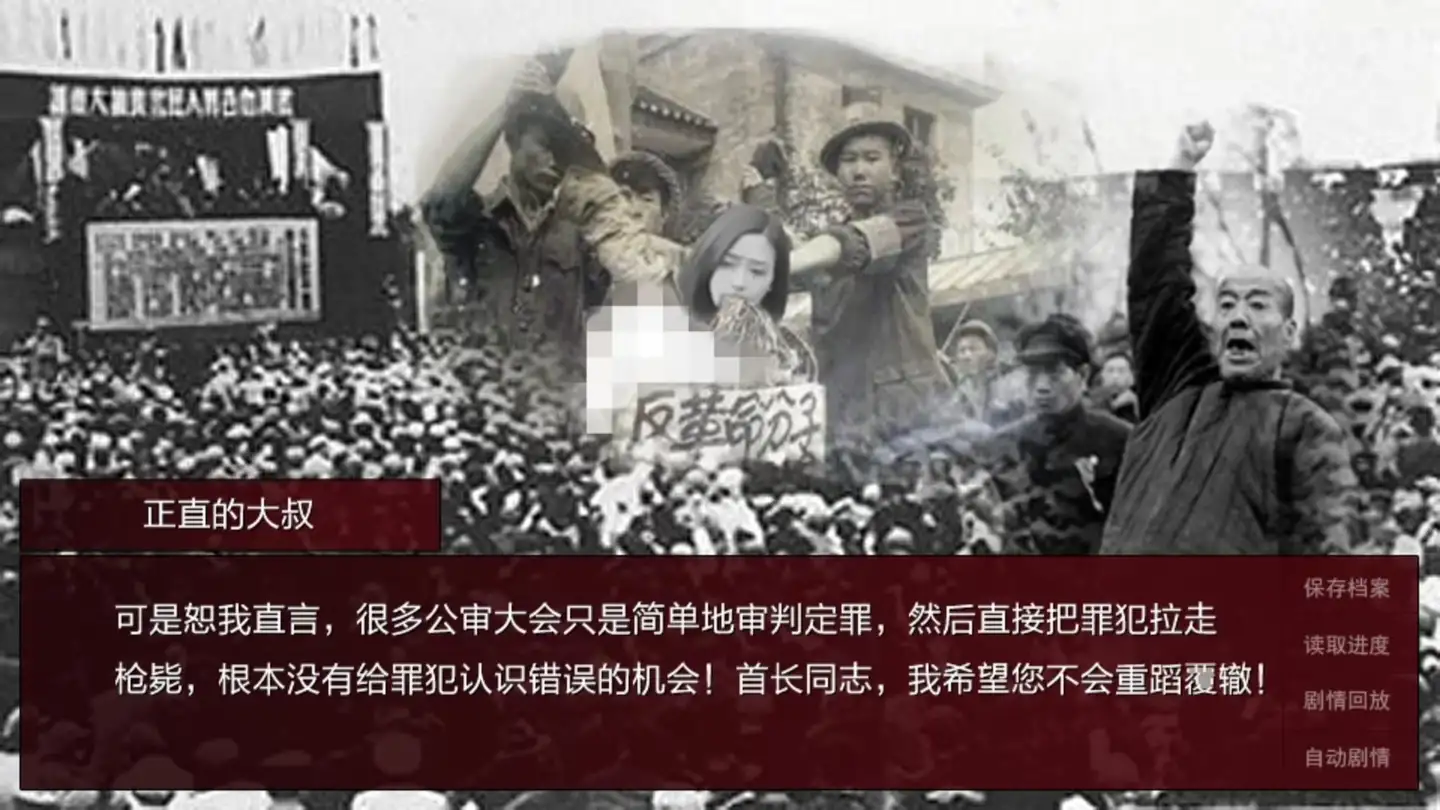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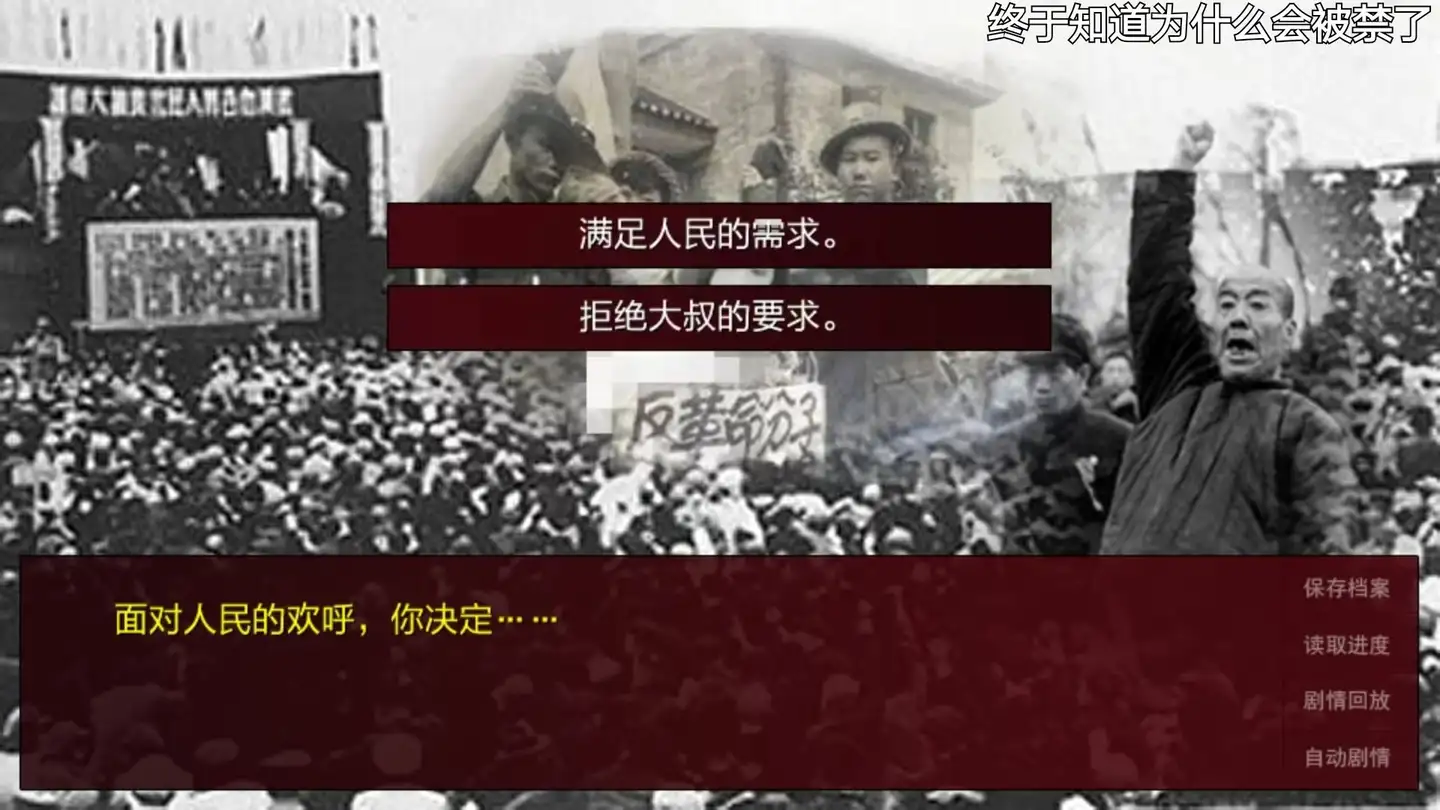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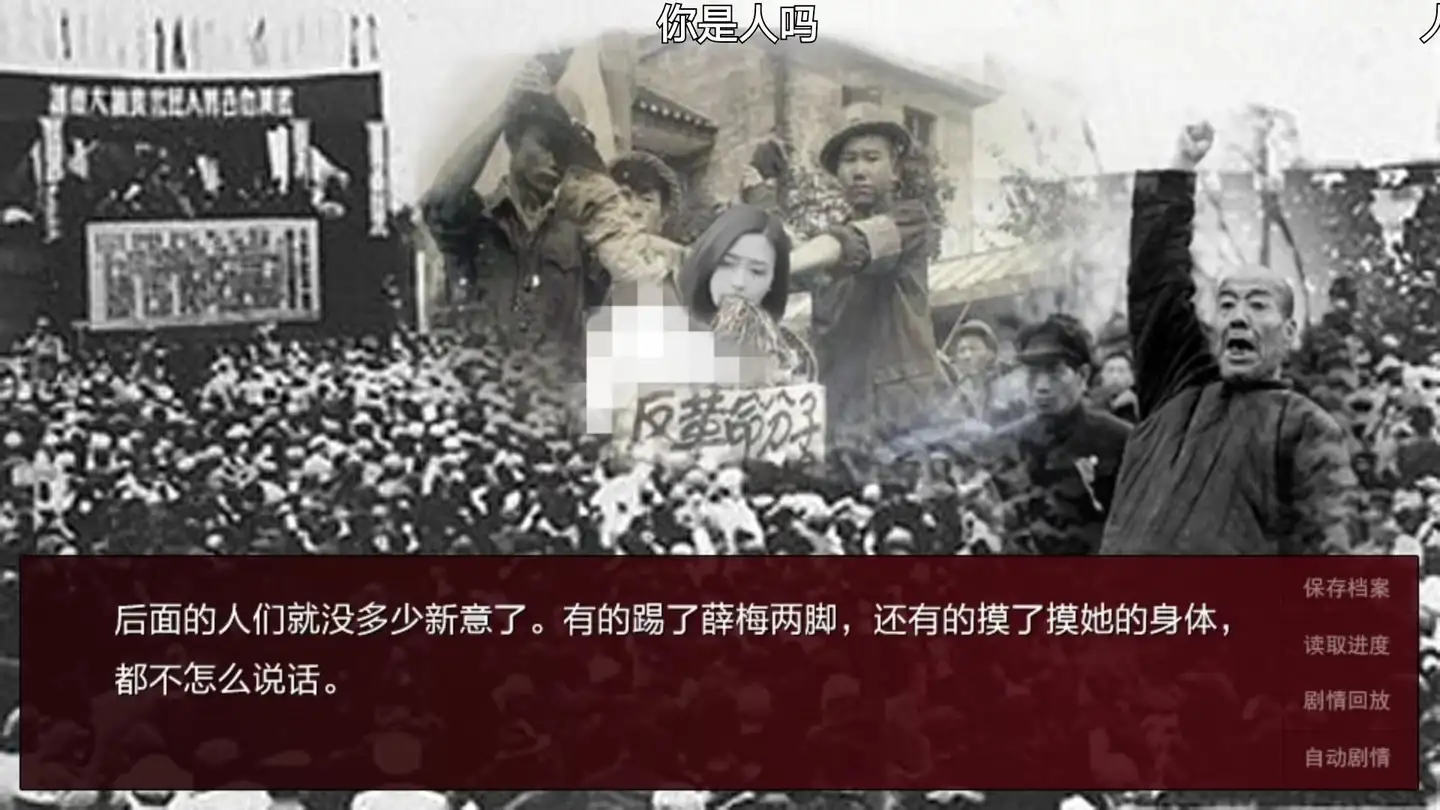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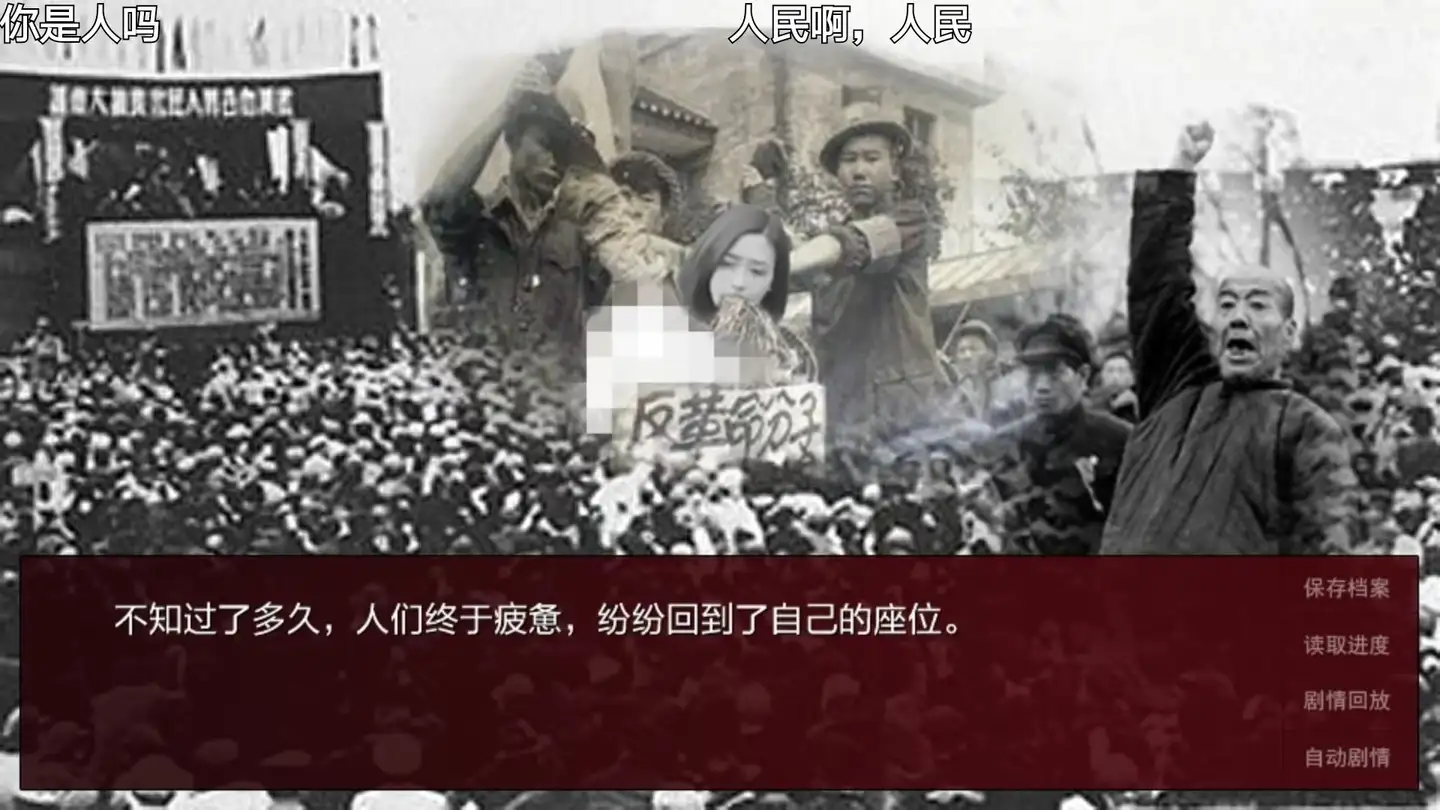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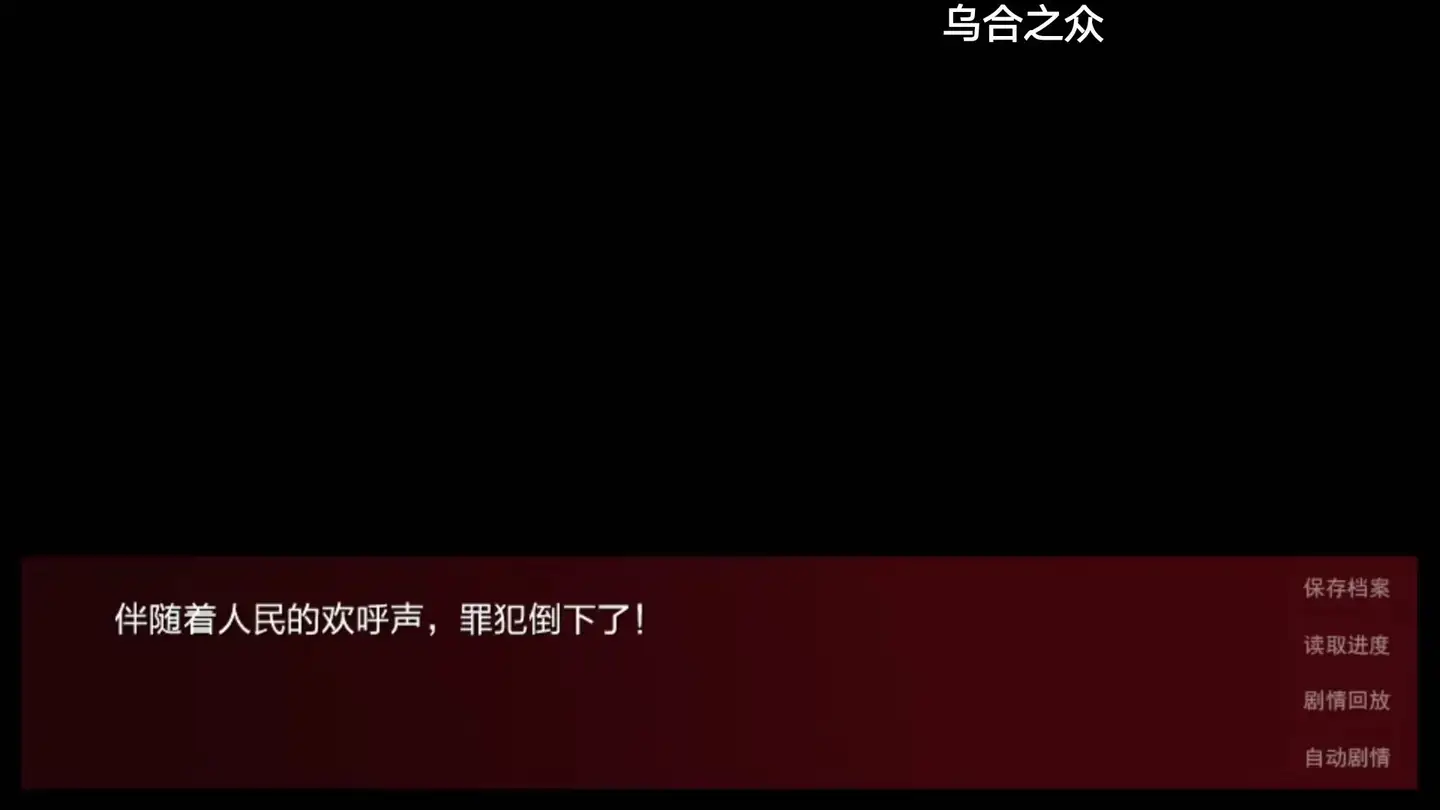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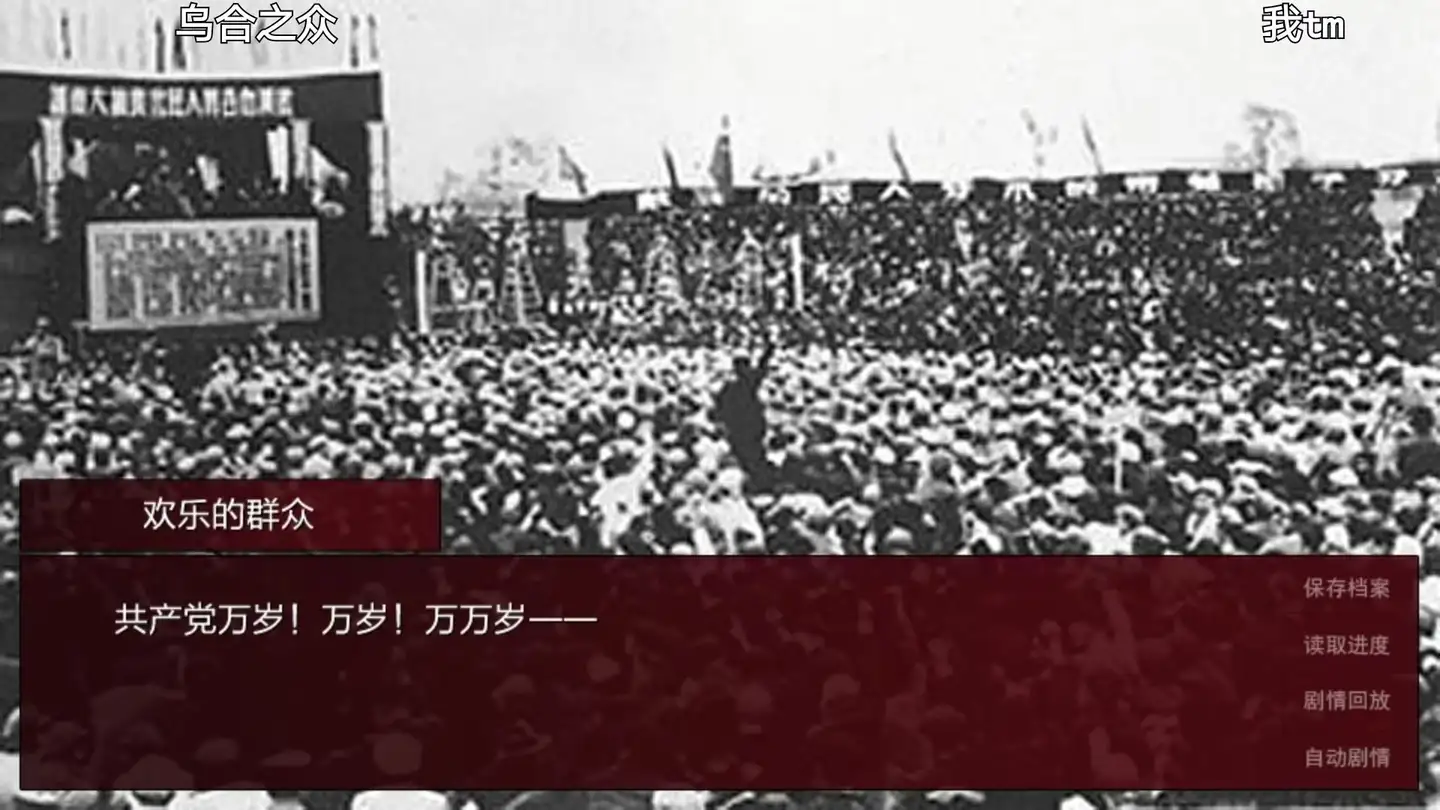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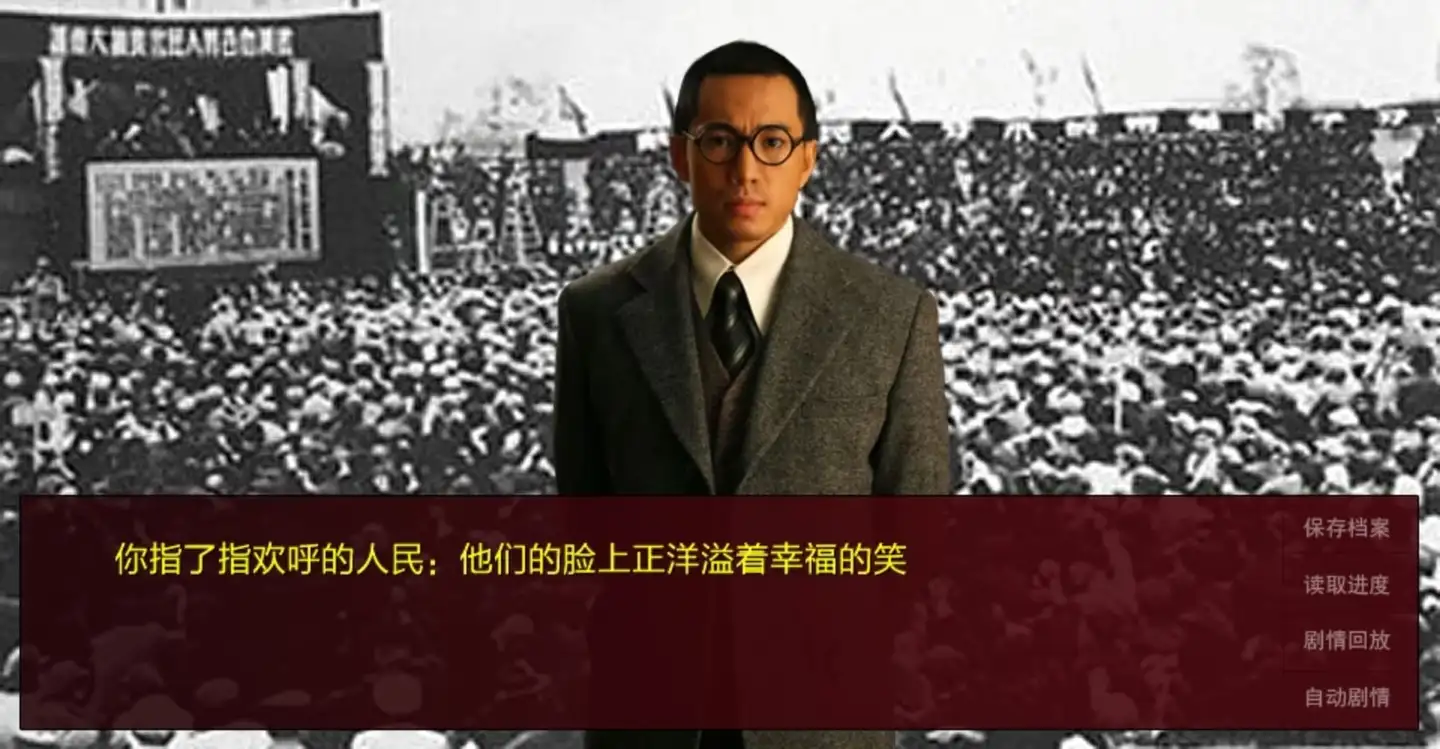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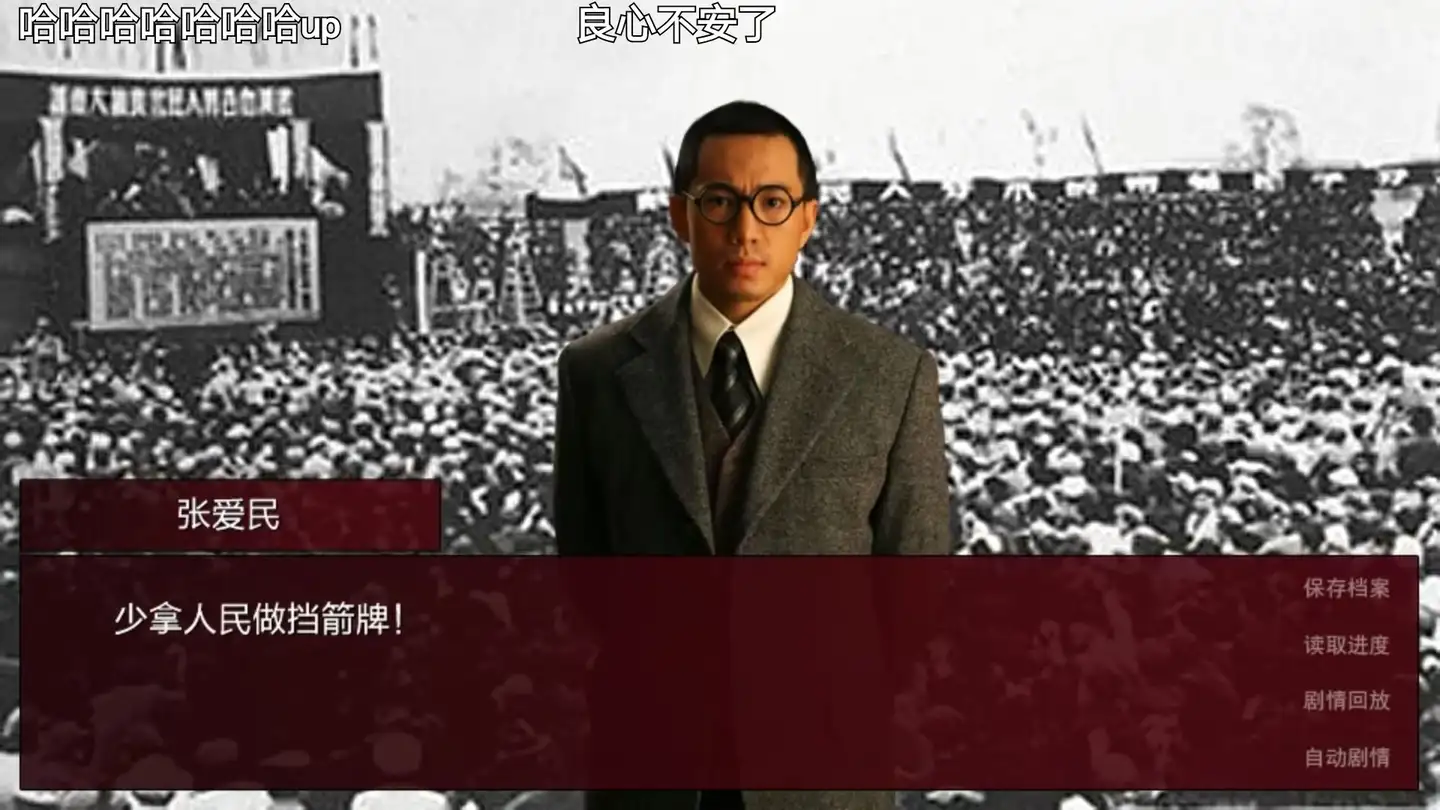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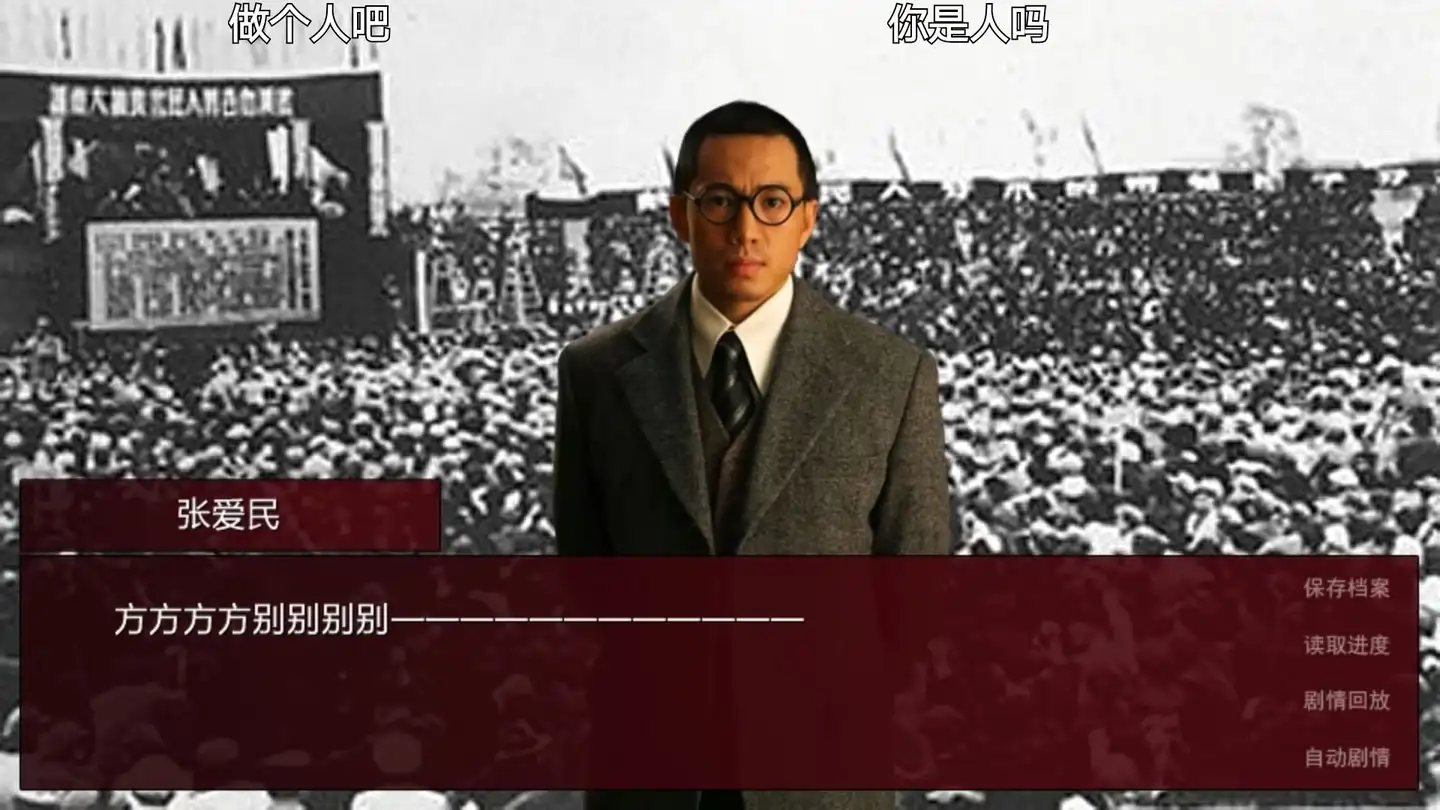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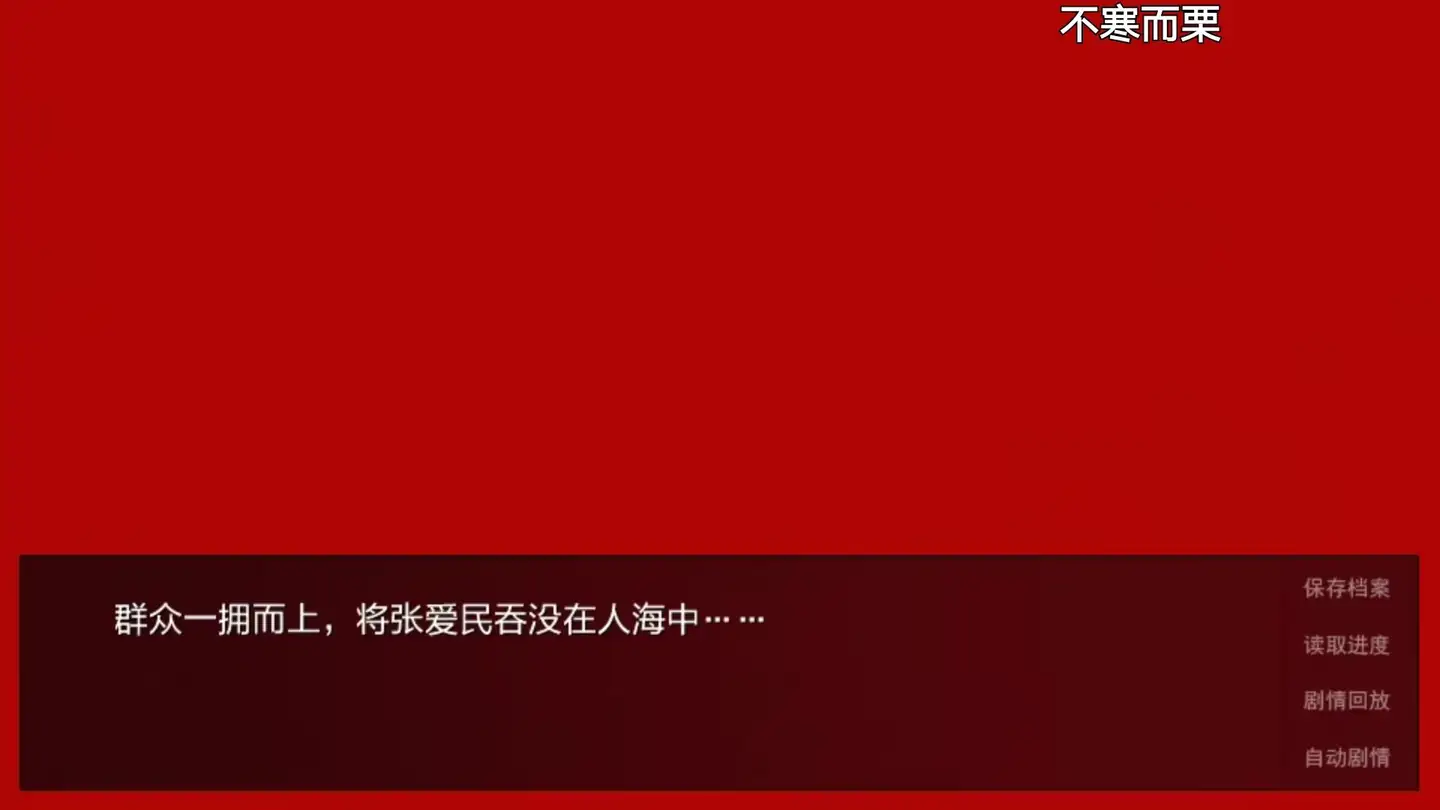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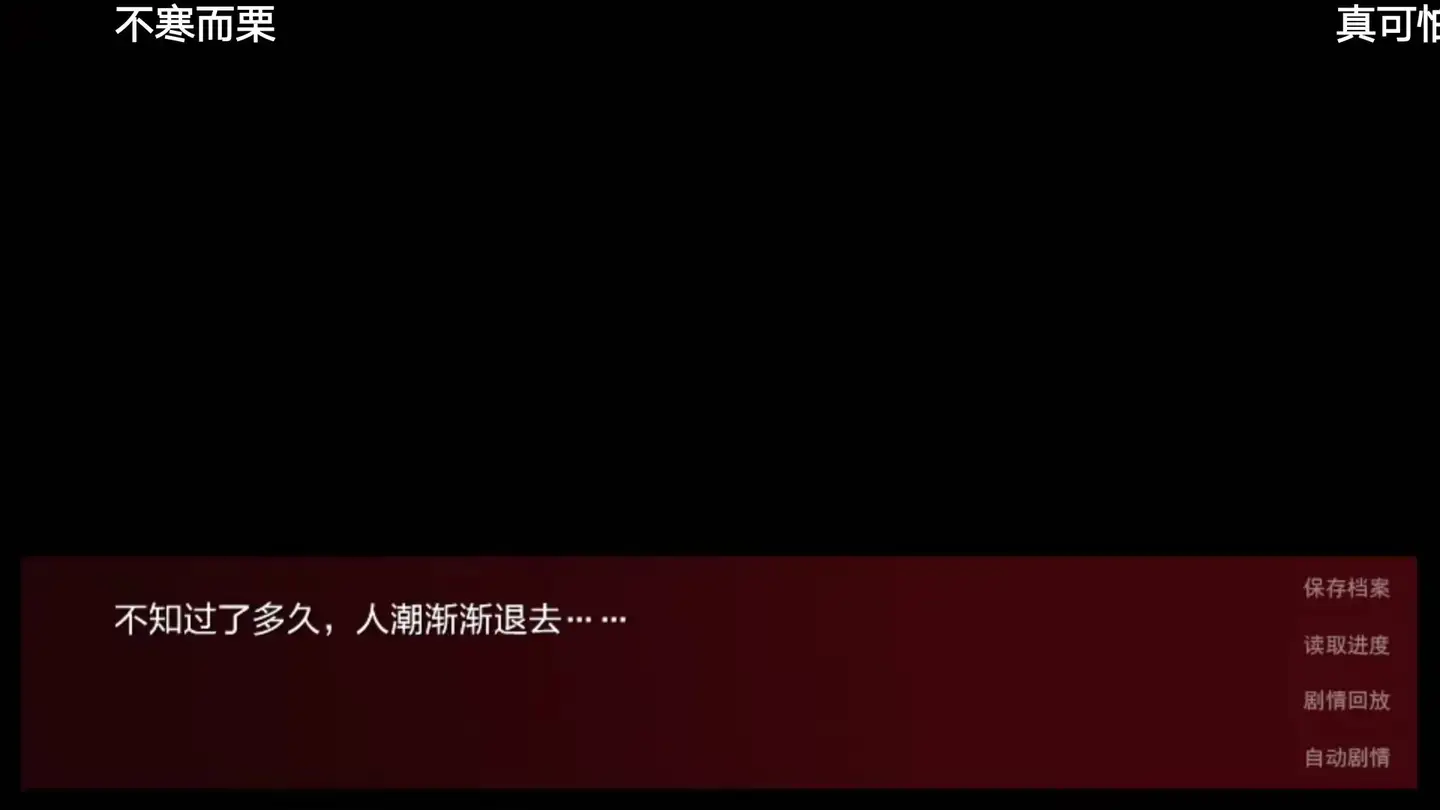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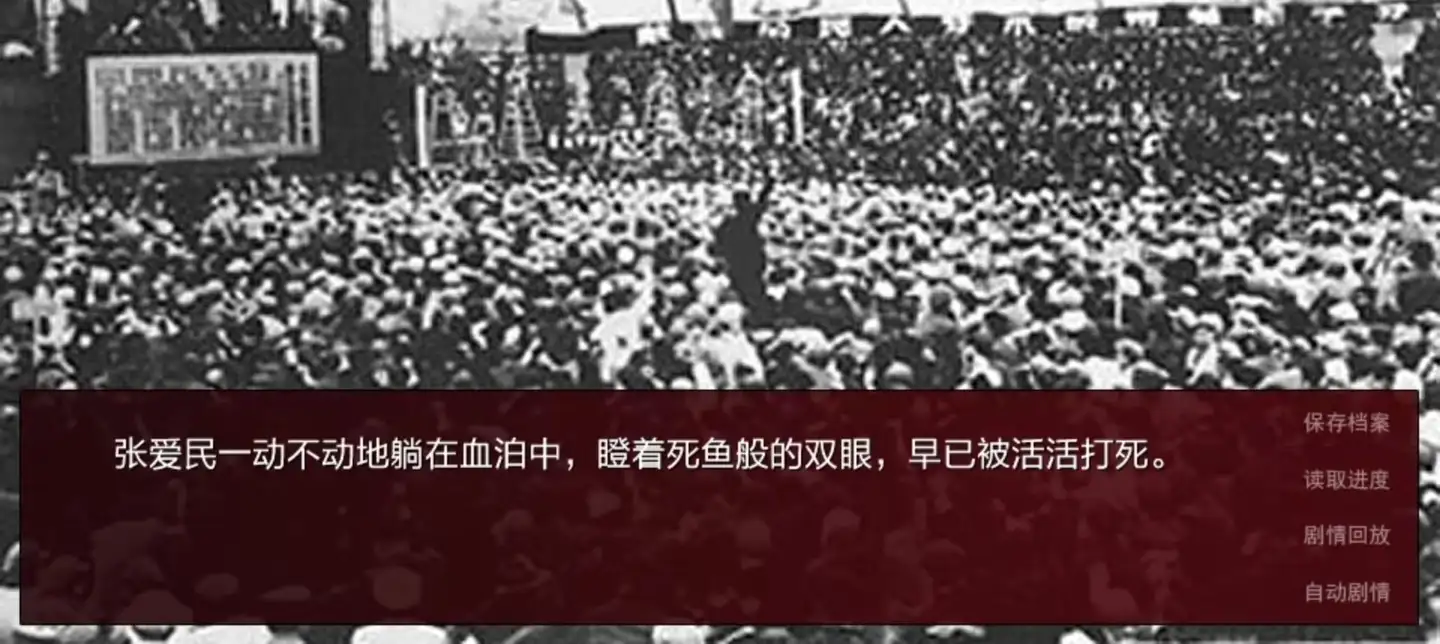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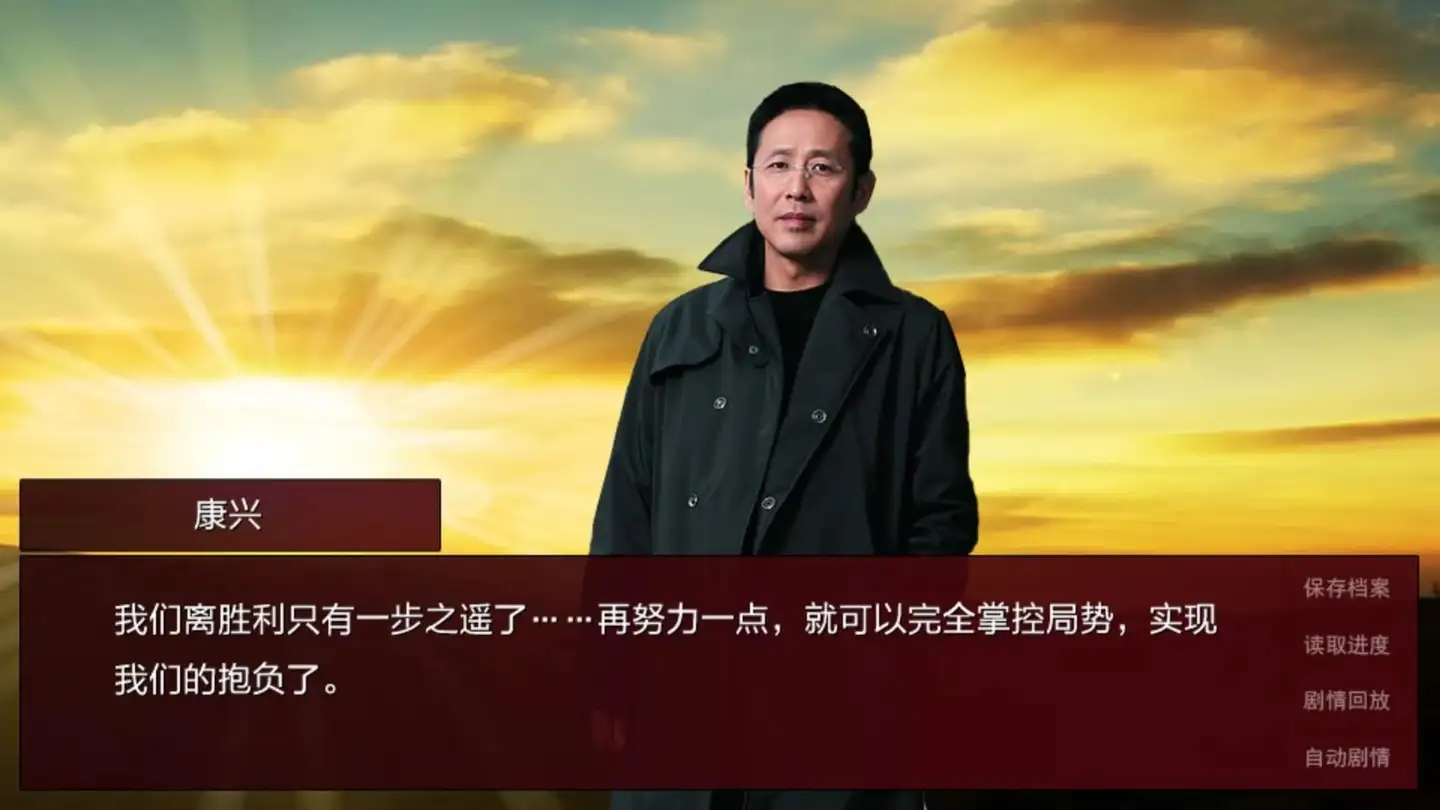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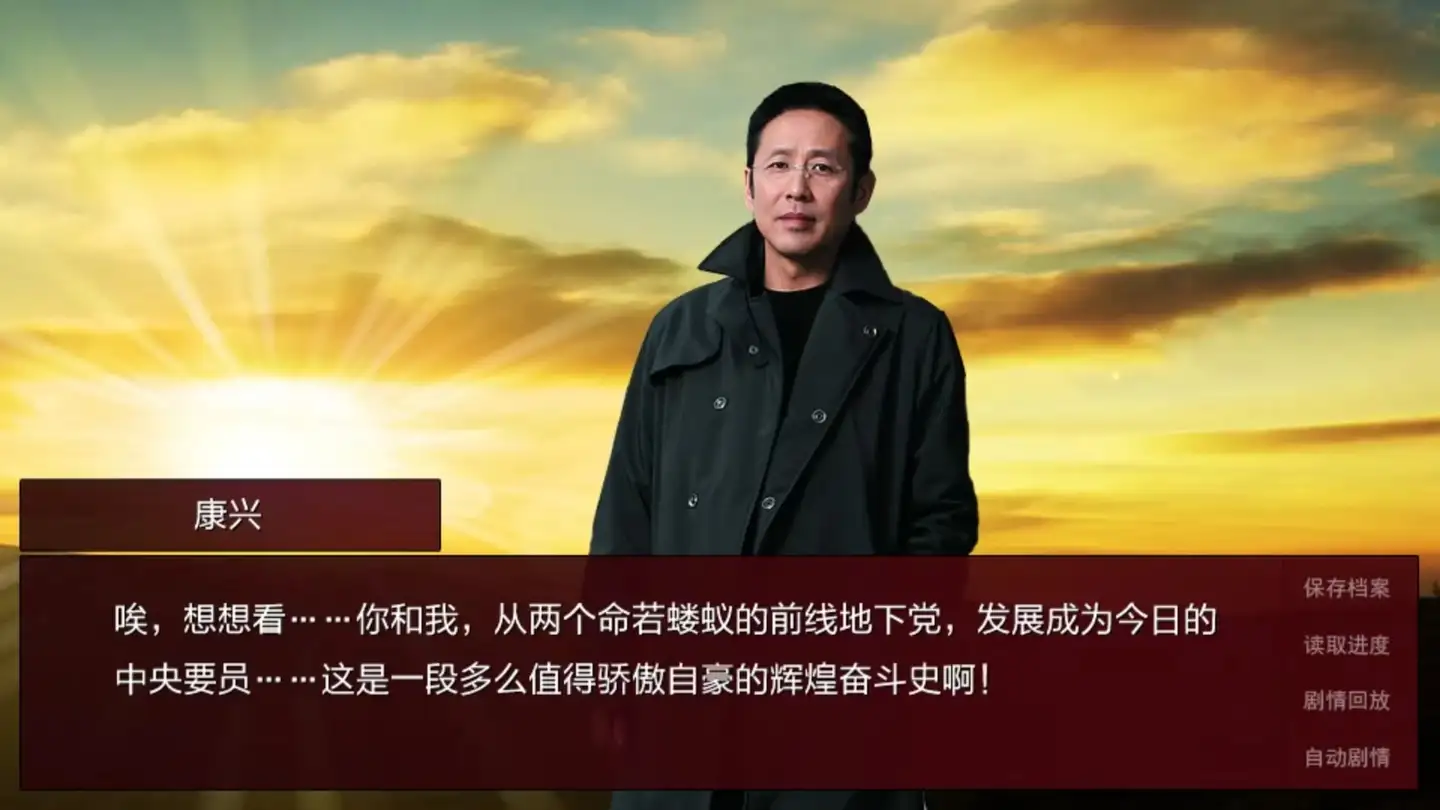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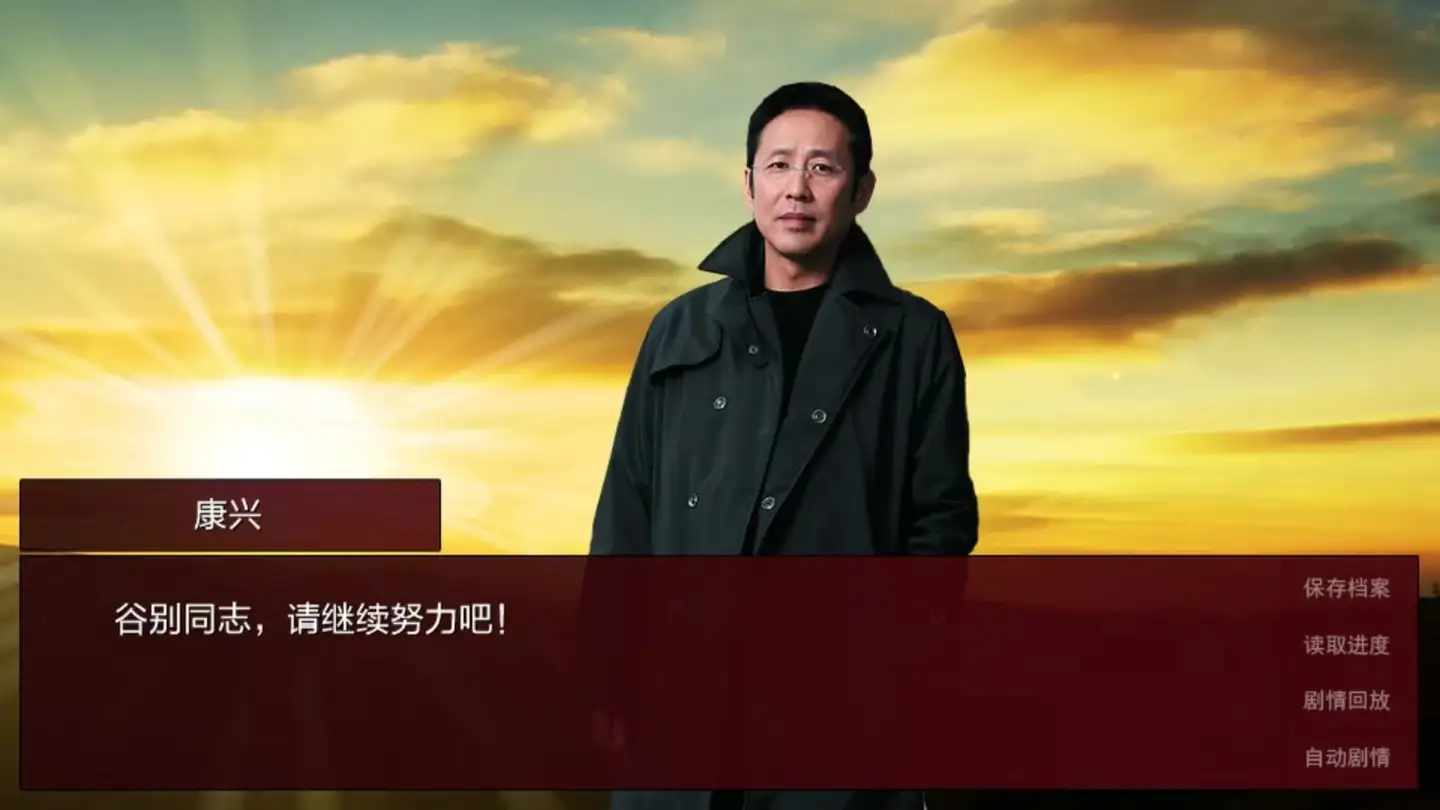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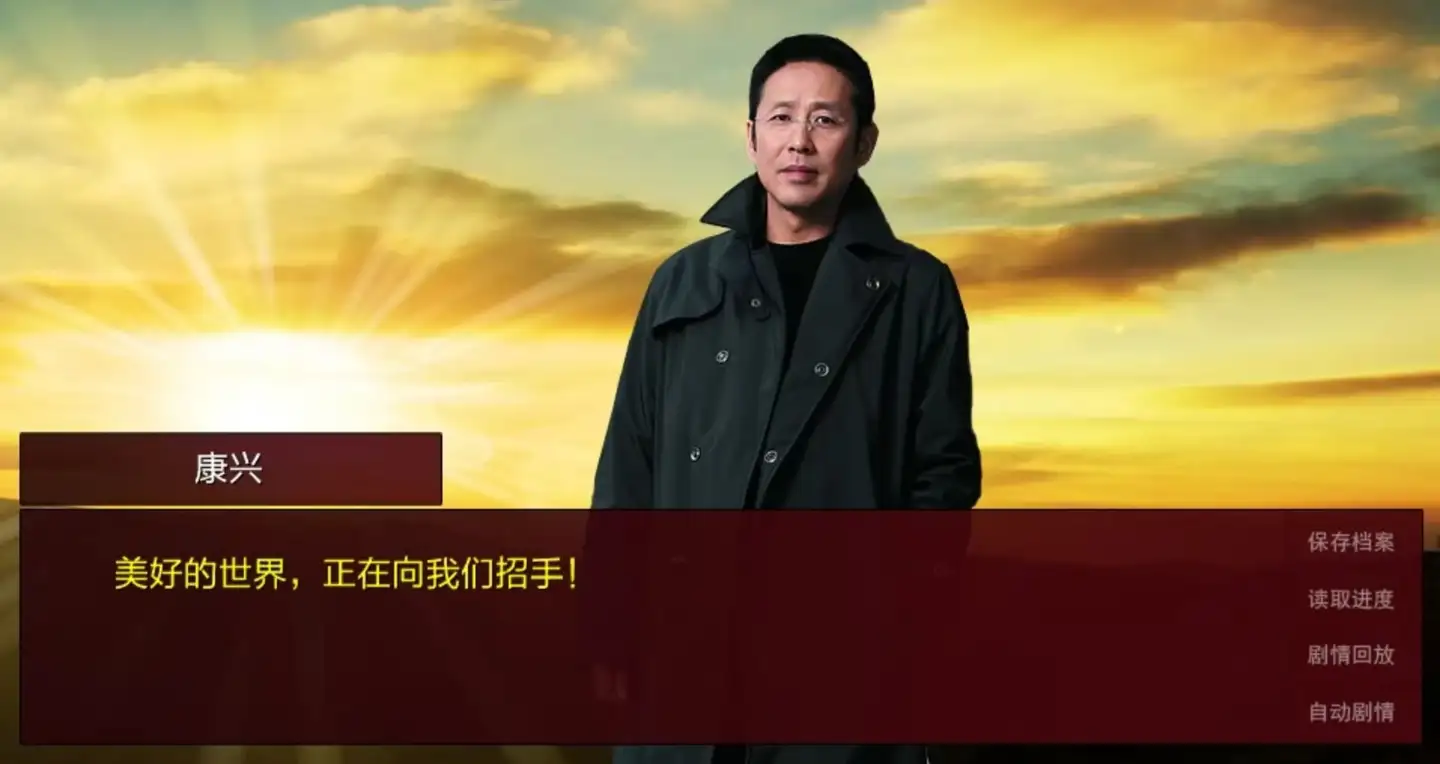
MSA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可参照Youtube视频——犹太裔作家David Horowitz在UCSD回答MSA组织成员提问
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UvJql3QIYM
Four Essays on Liberty
In Defence of Freedom: Six Enemies of Human Liberty
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
Intellectuals: From Marx and Tolstoy to Sartre and Chomsky
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
大国政治的悲剧
- 简介
- 主要观点
- 现实主义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理论(代译序)
- 中文版前言
- 英文修订版前言
- 英文出版前言
- 致谢
- 第一章 导论
- 第二章 无政府状态与权力竞争
- 第三章 财富和权力
- 第四章 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
- 第五章 生存战略
- 第六章 行动中的大国
- 第七章 离岸平衡手
- 第八章 均势与推卸责任
- 第九章 大国战争的原因
- 第十章 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
- 阎学通对话米尔斯海默:中国能否和平崛起?
- 译后记
简介
英文名: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作者:John J. Mearsheimer
John J. Mearsheimer is the R. Wendell Harrison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director of the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米尔斯海默将他的理论解释为“攻势现实主义”,源自早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他认为世界处于列强之间的冲突中,并且永远不会结束。
主要观点
无政府状态和权力斗争
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总是在寻找机会获得“力量”以超过它们的对手。他解释国家无休止的追求力量是因为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政府之上无政府”,没有一个守夜人能在国家遭受攻击时给予帮助,国家只能依靠其自身获得安全。因此,国家不断寻求扩大其自身的军事、经济力量以保障自身的安全。
陆地强国的首要地位
米尔斯海默认为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源于其军队的力量特别是陆军的力量,他认为陆军仍然是现代战争的主导力量,但陆军的投送能力受到广阔海洋的限制。另外,核武器能够降低但不能消除大国间陆军冲突的可能。
海洋的阻力
米尔斯海默认为海洋的存在让任何国家都无法实现全球霸权,他解释为海洋限制了军事力量的投射能力,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分散了霸权。
因此,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成为西半球的霸主,并防止在东半球出现类似霸主。换句话说,美国的角色是作为一个离岸平衡手,阻挠任何欧亚大陆霸权国家(俄罗斯、中国)的崛起,并且用战争作为阻止其崛起的最后手段。
离岸平衡手
米尔斯海默总结欧洲史上英国在欧陆的外交策略为离岸平衡,并指出美国应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
攻势现实主义
针对大国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作者采用的是攻势现实主义,在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下,大国首要关心的元素为如何在国际政治中生存。在攻势现实主义的解释当中,大国会为了自身的生存竭尽心力的扩充自身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对权力以获得最大的安全,故大国会为了自身不得不采取侵略性行为,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更多的权力。
现实主义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理论(代译序)
【注:先吐槽一句,大陆的国际关系搞得一塌糊涂,和各种国际关系专家脱不了关系。这里勉强记录点我觉得还行的内容,但这不代表我同意这些看法。这些内容仅供参考。】
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性
思维起点:神性——人性——国家性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起点:人性本恶,故权力本恶;国内是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国际是民族国家林立,势力均衡。人是自私的、理性的,故国家是利己的、理性的。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国家对权力、利益、安全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导致权力、利益、安全的稀缺性。人性的张扬导致国家性张扬,西方基督教内部血腥拼杀,对外则是野蛮扩张、掠夺、殖民。这就产生出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逻辑:以权力追求安全,以实力争取利益。
思维方式:国内——国际二分法
为了表明人性张扬导致的国家性张扬合法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杜撰出一个先验论——无政府主义(Anarchy),以便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区别开来——其本质是国际关系缺乏国内那样的中央政府权威,并非真正的无政府(Chaos)或无序(Disorder)。望文生义的翻译常常导致对西方理论的误解。其实国际关系中仍然是有法则的,古典现实主义推崇实力均衡法则就是对自然界平衡法则的延伸。因此,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描述的国际社会并非无法无天,现实主义各流派对国际法、国际道德、国际规范也是承认和尊重的,只是从根本上不相信它们能维护安全、保护利益而已——权力才是根本的。假定”无政府状态“是为了引进”自助体系(Self-help)概念。民族国家的结盟(Alliance)、跟着强者走(Band-wagon)、均势(Balance of power)等逻辑就是在“天助自助之人”的信念下展开的。……
现实主义的挑战者——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在修正“无政府状态”假定和“国内-国际”二分法,然而本质上并未动摇其逻辑,而是国际关系下不完全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关系的折射及西方无法主导世界的反映,但毕竟国际社会迄今未走出西方世界或西方化世界的影子。因此,现实主义仍然是最有说服力的,在中国也是信徒云集。
思维过程:原罪论导致宿命论
【注:中美冲突不可避免——其实不用等到现在,杜鲁门、马歇尔当年使劲坑害中国人,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性
国有际吗?国际有关系吗?国际关系有理论吗?
Nation-state在日文里翻译为国民国家,的确更贴切。此外“际”是否为“inter”,而不是“intra-national”、“trans-national”、“super-national”relations呢?
作为世俗文明的中国不会产生西方那样的国际关系理论,这就不足为怪了。所谓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只是模糊认识;本质上,在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性,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不以national-state为基本单元探讨国际关系理论,这就有待后西方世界的真正来临。
现实主义何以回归现实世界
《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将第十章改写为“中国能和平崛起吗?“是将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最终检验。
写序作者论文
大国政治的悲剧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剧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解析
王义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国际关系是以国与国关系形式表现的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与国内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国 内是有政府状态的,而国际社会是缺乏最高权威,处于无政府状态。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 国家追逐的基本目标是生存与发展,以国际关系术语讲主要是安全与权力。国际关系理论的 不同学派及其争论首要的即是围绕权力与安全的关系而展开。认为只有争取权力(强权)才 能追求到安全(和平)的是经典现实主义(以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为代表 ),认为各国权 力必须受制于集体安全与国际道德的是理想主义(威尔逊“十四点计划”),及至集体安全(世 界和平)与国际道德(国际法)以国际(内)制度、国家间相互依赖及国际组织等来体现, 理想主义又发展到自由主义阶段,并派生出国际制度和平论(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 和平论、国际组织和平论等不同主张(拉塞特《三角和平:民主、相互依赖与国际组织》)。
米尔斯海默在书中强调,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因为大国对国际政治所发生的变故影 响最大。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次大国——其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实力国 家的决策和行为。” 那么,何谓“大国”呢?
“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 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具备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常规战的能力。”
大国政治为何处于一种悲剧状态?因为“大国注定要进犯他国”。所谓“悲剧”,其涵义 有二:其一,大国安全竞争是零和博弈——这是悲剧的必然性:“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 酷而危险的交易,而且可能永远如此。……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 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然而,大国……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权, 即体系中惟一的大国。”
其二,国家的进攻性企图与权力和生存之间的不恰当紧密结合导致悲剧的恒久性:“国 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除了那种想对潜在的对手保持支配地位的一时霸权。大国很 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它 们几乎总是拥有修正主义意图,倘若能用合算的代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改变均势…… 除非一国达到了最高的霸权目的。然而,由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霸权,因此整个世 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 这种悲剧的持久性是以其彻底的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即不管 大国的性质如何,都会遵循这种逻辑。
总之,《大国政治的悲剧》从历史的长时段出发,认定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大国的生 存意志是追求自身权力最大化,即地区霸权,因而大国间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冲突。而由于中 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中美冲突将不可避免。中国会和当年的美国一样,提出亚洲版本的门罗 主义,将美国赶出亚洲,因而主张及时限制中国发展,反对接触而主张遏制中国。
书中,作者根据“引起国家争夺权力的原因是什么”、“国家想要多少权力”将现实主义分 为人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
人性现实主义,有时又被称作“经典现实主义”。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一书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他在该书中将国家性等同于人性,强调国家的“权力欲望”,认为国际政治的主 要驱动力是体系中的“权力意志”。
防御性现实主义又常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主要体现在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 中。与摩根索不同,华尔兹并不认为国家内在的侵略性是由于被灌输了权力意志,而在于追 求“生存”这一目标,无政府状态鼓励国家采取防范措施,使其维持而不是打破均势,因为“过 多的权力”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联合抗衡。因此,守住权力而不是增加它才是国家的主要目标。
围绕冷战结束的争论,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 以及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通过集中关注名为“进攻-防御平衡”的结构概 念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个案提供支持。他们指出,无论何时,军事力量都被划分为要么偏重 进攻要么倾向于防御两类。倘若防御明显强于进攻,征服将变得困难,那么大国就不会萌发 用武力攫取权力的动机,而是保护它们已经拥有的权力。当防御占优势时,保护已有的权力 就更为容易。相反,倘若进攻更易于得手,国家就非常渴望征服他国,那么体系中出现频繁 的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不过,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进攻-防御”平衡常常向防御的方向严 重倾斜,从而让征服变得极其困难。总之,建立充分的均势加上防御比进攻所具有的自然优 势,应该能打消大国寻求侵略战略的念头,而使其成为“防御的倡导者” 。
作者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分道扬镳 了。对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而言,国际结构几乎不为国家提供任何寻求权力增生的诱因,相反 它促使国家维持现有的均势,守住权力而不是增加它才是国家的主要目标。而在进攻性现实 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原因是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 得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一国的终极目 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
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强调国际体系的霍布斯主义性质,在他们看来,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 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结果 便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正如米尔斯海默所指出的:“国家最初的动机是防御性的,但国际 体系的结构迫使国家去作进攻性思考,有时则采取进攻性行动。”
追求霸权的国家为什么不担心其他国家会组成均势联盟反对它呢?作者指出:“受威胁 的国家常常会采用推卸责任而不是均势战略,因为在战争爆发时,推卸责任者可避免与侵略 者打斗的代价。” 这就突破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本书一再强调,国际体系结构是通过世界是如何组成的五个假设来界定的,包括如下的 几点事实基础:(1)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者,处于一个无政府体系中。该体系缺乏 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并能保护彼此不受侵犯的中央权威。(2)大国都具备一定的进攻性军事 能力。(3)一国无法确定他国是否怀有敌意。(4)大国高度重视生存。(5)国家是理性行 为者,能理智而有效地设计使其生存机会最大化的战略。
作者指出,上述五条中的任何单一命题都不能千篇一律地保证大国彼此“应该”采取侵略 举动。不过,当五个命题同时具备时,它们就为大国萌发并采取针对他国的进攻行为创造了 强大动力,尤其可能出现三种总的行为模式:畏惧(fear)、自助(self-help)和权力最大化 (power maximization)。
第一,大国彼此畏惧。它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对方,担心战争迫在眉睫,国家之间几乎没有信任的余地……任何大国都认为所有其他大国是潜在的敌人。 畏惧的根源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攻击能力和不信任。当一个国家受到威胁时,没有国 家之上的权威机构帮助它,也没有任何方式使侵略者受到惩罚。因此,它们不得不随时为战 争做准备。
第二,自助原则。由于政府之上没有政府,因此,国家彼此皆为潜在的敌人,不能依赖 别人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必须自己帮助自己。在国际政治中,天助自助之人。自助原则并不 排斥国与国之间建立联盟,但是联盟是暂时的,是权宜之计。今天的盟友可能是明天的敌人, 今天的敌人也可能是明天的盟友。
第三,权力最大化原则。由于惧怕他国,国家必须自助,因此,大国最佳的安全保障就 是成为系统中最强的国家,一国越是强于对手,它受攻击的可能性就越小。国与国之间的实 力相差越大,强国受弱国攻击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理想的局面就是成为系统中的霸主。
作者进而总结道:“进攻性现实主义主要是一种叙述性理论。它解释大国过去如何表现 以及将来可能怎样行动。但它也是一种指导性理论。国家‘应该’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意旨 行事,因为它展现了国家在险恶的世界里求生存的最好办法。”同时他又提醒道,“进攻性现 实主义如同黑屋子中的一道耀眼的亮光:即便不能照亮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但在大部分时间 内它仍是引导人们穿越黑暗的极好工具。”
……
作为一般理论的普遍缺陷,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保留并强化了现实主义的传统 与偏颇,如对国内政治的忽略,静态化地理解国际无政府状态,忽视国际机制、非国家行为 体的作用,过分强调国家权力、安全最大化原则,未认识到大国扩张的边际效用原理——“当 边际成本高于边际收益时,大国便会停止扩张” 。
……
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十分强调陆地力量的重要性,认为作为军事权力原动力的 人口与财富是衡量大国的主要标准。大国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地区霸权,但不可能形成全球霸权,原因是越过巨大的水域投送力量十分困难:“巨大的水体使陆军很难进犯一个由武装完 备的大国保卫的领土。”
这样,陆地逻辑形成的进攻性原则与水体阻遏力量之海洋逻辑的结合,使“离岸平衡手” 角色成为大国的最佳选择,如此方能超越均势联盟的制约;作者还认为,美国是现代历史上 惟一成功获得地区霸权的国家,尽管其他国家为了寻求地区霸权打过许多大仗,如东北亚的日本帝国、欧洲的拿破仑法国、威廉德国和纳粹德国等,但没有一个获得成功。取得地区霸 权的国家,常常试图阻止其他地区的大国续写它们的业绩。换句话说,地区霸权不需要与之 匹敌的对手:“难怪美国这个现代历史上惟一的地区霸权从未考虑过征服欧洲或东北亚。一 个大国可以征服它从陆地上能到达的相邻地区,但是绝对不可能获得全球霸权。” 笔者曾 经指出,这种“离岸平衡手”本身是美国作为“霸权均势”角色的重要体现:从内部看美国,它 是“离岸平衡手”,而从外部看则完全相反,让人感到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全球霸权。
在作者看来,美国是历史上惟一成功获得地区霸权的国家以及越过巨大水域投送力量十 分困难这两个事实,使得美国作为两面靠洋(既非欧洲亦非亚洲)的大国地位永远无法动摇, 换句话说,其霸权将永世长存,“因为两个庞大的‘护城河’——大西洋和太平洋——一直把它 与世界其他大国分隔开来,因此,美国也许是历史上最安全的大国,” 这体现了进攻性现实 主义的保守性。这样,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避免了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所警告的帝国“过度扩张”的灾难,超越了历史上大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的钟摆逻辑。
理论的种种不足往往与理论本身折射出的作者个性、国家性与时代性分不开的,因此, 笔者提倡以“作者个性-—国家性-—时代性”三个层面评判理论。从作者个性来说,本书对 权力的理解特别亲睐于领土征服与陆地力量,过分强调越过大片水域投送力量的困难。这恐 怕与作者的经历有关。作者西元1970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后在美国空军服役 5 年。如果他是毕 业于海军学院,在航空母舰服役,是否还会坚持“越过大片水域投送力量的困难”呢?作者的 其他个性,包括其悲剧意识、历史哲学,无疑也对其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作者经历严重影 响其理论特色与偏颇的类似局面也可从摩根索、基辛格等人身上找到——作为犹太人的传统悲观思维与二战的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两人的现实主义理论观。
在国家性方面,非常有意思的是本书第一章末尾对美国领导人惯于言行不一的现象分 析。作者认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深处是自由主义的,但往往根据现实主义行事,美国是说一 套做一套的。这就统一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所谓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分野的认识。 更有启发意义的方面在书中并未挑明,那就是,这一逻辑分裂是美国精神世界的“例外论”思想在作祟。
为美国度身定做的“离岸平衡手战略”与布热津斯基的欧亚“大棋局”战略有异曲同工之 趣,分别代表了海洋与陆地两种版本的霸权均势战略。因而米氏提出“大国政治的悲剧”这一 耸人听闻的逻辑,目的在于“为永葆美国强权开药方”。
中文版前言
《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中心思想是,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即便满足于和平生活的国家也会被指责参与了无情的权力竞争。
他们一定已注意到,美国的精英们常常用理想主义术语谈论外交政策, 却以现实主义方式形式。
【注:民主党人的理想主义不知坑害了多少地球人,哎!】
英文修订版前言
【注:美国主要欺负小国,有效反驳姨粉分裂论。】
英文出版前言
例如,我强调大国追求使其分得的世界权力最大化。我还认为,包含一个特别强大的国家,换句话说,包含一个潜在霸权国家的多级体系,特别倾向于战争。
致谢
第一章 导论
作者先引福山”历史的终结“的相关言论——认为和平永降人间的时代开始了,但作者不同意这个看法。
悲哀的是,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而且可能永远如此。虽然大国竞争的烈度时有消长,但它们总是提防对方,彼此争夺权力。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然而,大国不只是为了争当大国中的强中之强,尽管这是受欢迎的结果;它们的最终目标是是成为霸主(Hegemon),即体系中唯一的大国。
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除了那种想对潜在的对手保持支配地位的一时霸主。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它们几乎总是拥有修正主义意图,倘若能用合算的代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改变均势。有时,当大国认为改变均势的成本过于高昂时,它们不得不坐等更有利的形势,但猎取更多权力的欲望不会消隐,除非一国达到了最高的霸权(Hegemon)目的。然而,由于任何国家取得全球霸权,因此整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
这种对权力的无情追逐意味着大国可能倾向于伺机使世界权力的分配朝有利于大国的方向改变。一旦具备必要的实力,它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简言之,大国存有进犯的预谋。然而,一个大国为了获取权力不但要牺牲他国利益,而且会不惜代价阻止对手获得权力。因此,当权力隐约出现有利于另一国的变化时,大国会极力捍卫均势;而当有可能出现有利于本国的变化时,它就会抓住机会,想方设法打破平衡。
为什么大国会如此表现呢?我的答案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一心寻求安全的国家彼此采取侵略行为。国际体系的三个特征一并导致了国家间的相互提防:(1)缺乏一个凌驾于国家至上并能保护彼此不受侵犯的中央权威;(2)国家总是具有用来进攻的军事能力;(3)国家永远无法得知其他国家的意图。有了这一担心——不可能完全一劳永逸地消除——国家认为实力愈是强于对手,自己生存的几率就愈高。毫无疑问,生存的最高保证是成为霸主,因为再没有其他国家能严重威胁此类巨无霸。
没有人有意预设和构想这种局面真是一个悲剧。虽然大国没有理由彼此攻击——它们只关心自己的生存——但在该体系中,它们除了追求权力和征服其他国家之外别无选择。在该段的下半段,作者引用了俾斯麦评价波兰人的例子证明上述观点。
进攻性现实主义
关于大国关系的互动,作者提出了一系列观点,特别强调它们寻求机会来攫取权力,损人利己。另外,我区分了最易和最难引发冲突的情况。譬如,作者认为多极体系比两极体系更容易导致战争,而含有特别强大的国家,或曰含有潜在霸主的多极体系是众体系中最危险的体系。
大国主要是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在一场全面的常规战争中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进行一次正规战斗的军事实力。候选国家不一定具备打败领先国家的实力,但它必须具有把冲突转向消耗战并严重削弱优势国家的潜能,即便优势国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在核时代,大国不仅要拥有令人生畏的常规力量,而且还必须具有能承受他国核打击的核威慑力。但也不排除这一可能:一国拥有超过其他所有对手的核优势,它非常强大,在该体系中称霸世界。如果体系中出现了核霸权,那么常规武力均势在很大程度上就显得无关紧要。
理论的价值与局限
进攻性现实主义主要是一种叙述性理论。它解释大国过去如何表现以及将来可能怎样行动。但它也是一种指导性理论。国家”应该“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因为它展现了国家在险恶的世界里求生存的最好办法。
追逐权力
权力是作者论点的实质。
对于所有现实主义者来说,盘算权力是国家考虑周围世界的关键所在。权力是大国政治的货币,国家为之争斗。
本书围绕六个问题对权力展开讨论。第一,为什么大国想要权力?国家争夺权力的根本逻辑是什么?第二,国家想要多少权力?多少权力才是足够的?这两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关系到大国行为的最根本问题。如上所述,我对这些问题给出的答案是,国际体系的结构鼓励国家追求霸权。
第三,什么是权力?这一核心概念是如何定义和度量的?有了好的权力参照点,才可能确定个别国家的权力水平,然后我们就能描绘该体系的架构,特别是认定哪些国家具备大国资格。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确定体系是霸权(由单一大国主导)、两极(由两个大国控制)还是多极(有三个或更多大国主宰)体系,而且还可得知主要大国的相对力量。我们尤其想弄清它们的权力是否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均衡分配或存在极大的不对称性,特别是体系内是否存在一个潜在的霸主——一个比它的任何大国对手都强大得多的国家。
同时,明确地定义权力还可为我们考察国家行为提供一个窗口。如果充分了解权力的内涵,一旦国家为权力竞争,我们对竞争的属性就懂得更多,进而得知展开竞争的原因。概言之,更多的了解权力的真实本质有助于解释大国之间如何竞争。
第四,当一个大国威胁要打破均势时,其他国家以何种策略获取或维持权力?讹诈和挑起战争是国家获取权力时所采取的主要策略,建立均势(Balancing)和推卸责任(Buck-passing)是大国面对危险对手时用以维持权力分配的主要手段。通过建立均势,受威胁的国家承担起阻遏对手的重任,并投入大量资源以实现这一目标。而通过推卸责任,处于危险中的大国设法让另一国承担起阻止或打败威胁过的重任。
最后两个问题集中讨论国家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的关键策略。第五,战争的原因是什么?何种权力因素使安全竞争的加剧及进而导致的公开对抗更容易或更难以发生?第六,在什么情况下,受威胁的大国会采取军事策略以对抗危险的敌手,又何时企图把责任推卸给另一受威胁的国家?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
作者认为的上个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三部现实主义著作:
- 卡尔《二十年危机,1919-1939》
-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
- 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
所有这三位现实主义大师在其作品中都批评了自由主义的某些方面。比如说,卡尔和华尔兹对自由主义关于经济相互依存提升和平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同时,这些现实主义者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如华尔兹挑战摩根索关于多极比两极体系更为稳定的论点。另外,虽然摩根索认为国家努力争取权力是由其本能的贪欲使然,但华尔兹却坚持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国家追求权力以提升它的生存前景。这些事例只是现实主义思想家众多分歧的缩影。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对国际政治的乐观建立在三个核心信念之上,这些信念是该理论所有流派耳熟能详的共识。
第一,自由主义者把国家看成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
第二,国家的内部属性存在很多变数,其差异对国家的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此外,自由主义理论家常常认为,有些内部安排(如民主)天生优于其他因素(如专制)。因此存在好与坏的国家,好国家寻求合作政策,彼此很少发生战争;而坏国家则挑起与其他国家的争端,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因而,通向和平的钥匙在于让好国家遍布全球。
第三,自由主义者相信,权力的多寡几乎不可能解释好国家的行为,它们对其他形式的政治和经济盘算更具重要性,尽管不同理论对盘算的方式各有不同。坏国家可能受贪欲驱使,为猎取权力而牺牲他国利益,但这只是因为它们被误导罢了。在一个只有好国家的理想世界里,权力基本上无关紧要。
衍生理论:
- 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国家间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使它们不可能彼此发动战争。
- 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不会对其他民主国家发动战争。
- 国际制度和平论:国际制度提升国家间的合作前景并能极其有效地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注:根据<独裁者手册>,如果民主国家的人民认为其他民主国家的行为有害,其实往往也是靠发动战争或支持军事政变来解决问题。美国经常干这事。】
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强调现存力量和趋势的不可抗力,并坚持认为最明智的选择是接受,并使自己适应这些力量和趋势。——卡尔
这一国际关系悲观论由三个核心要件组成。第一,现实主义者把国家看成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现实主义者重视大国,因为这些国家主宰和塑造着国际政治,同时也引发致命的战争。
第二,现实主义者认为,大国行为主要受其外部环境而不是内部属性的影响,所有国家必须面对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它们的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一般不对国家的”好“或”坏“进行明确划分,因为任何大国无论它的文化和政治体系如何,也不管它由谁来掌控政府,都会按照相同的逻辑行事。因此,国家很难被区分开来,唯独相对权力的差异例外。
第三,现实主义者认为,对权力的追求支配国家的思维,国家为权力而竞争。有时,竞争是战争成为必需品,战争被视为一种可接受的治国手段。……最后,竞争具有零和属性,又是非常惨烈和不可饶恕。当然,国家彼此也有偶尔的合作,但它们从根本上具有相互冲突的利益。
生存催生侵略行为。大国具有侵略行为并不是因为它们想要这样做或具有内在支配欲望,而是因为他们要想获得最大的生存机会,就不得不寻求更多的权力。下表概述了主要现实主义理论是如何回答上述基本问题的。
| 分类标准 | 人性现实主义 | 防御性现实主义 | 进攻性现实主义 |
|---|---|---|---|
| 引起国家争夺权力的原因是什么? | 国家内在的权力欲望 | 体系结构 | 体系结构 |
| 国家想要多少权力? | 所有能得到的国家使相对权力最大化,把霸权作为终极目标 | 不多于所拥有的国家注重维持均势 | 所有能得到的国家使相对权力最大化,把霸权作为终极目标 |
| 代表人物及其作品 |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 | 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 | 本书作者及本书 |
| 别称 | 经典现实主义 | 结构现实主义 | 无 |
自由美国的权力政治
现实主义理论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现实主义核心思想——为国家自私地追逐权力提供绝好的凭据——不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为什么美国人不喜欢现实主义
美国人也倾向于认为,道德应在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著名的社会学家西莫·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写到:”美国人是乌托邦式的道德家,他们试图让德行制度化、铲除邪恶的人并消灭邪恶的制度和实践。“(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p63)
【注:美国立国精神和儒家确实很接近!】
言辞与实践
美国学术界特别擅长提升思想市场中的自由主义成分。然而,关起门来,筹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却满口权力语言,而不是什么法则;在国际体系中,美国也在按现实主义逻辑行事。实质上,他们的公开言论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具体操作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
聪明的观察者应该清楚地注意到,美国是说一食,做一套。实际上,其他国家的决策者总在评论美国的这种外交政策倾向。例如,卡尔早在西元1939年就说过,欧洲大陆国家把讲英语的民族看成是“在善良的外衣下掩盖其自私的国家利益的艺术大师”,“这种伪善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思维中的特有怪癖”。
另外,美国本身对言辞与实际之间的这种差距是视而不见而。两种因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首先,现实主义政策有时与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一致的。……
其次,当美国处于权力考虑不得不采取与自由主义相冲突的行动方式时,”抬轿人“(spin doctors)就会出现,并会讲述一个与自由理想极为匹配的荒诞故事。例如,西元19世纪晚期,美国把德国看成是值得效仿的进步的宪制国家。但是,在一战爆发前十年中,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美国对德国的看法也改变了。直到西元1917年4月美国对德国宣战时,美国才不得不承认德国比他的欧洲对手更加专制好战。
【注:美国佬也曾崇拜德二,确实是个有趣的事情。】
同样,西元20世纪30年代晚期,许多美国人把苏联看成魔鬼国家,部分原因是由于斯大林在国内实施清洗政策以及他在西元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臭名昭著的互不侵犯条约。可是,当美国在西元1941年末与苏联联合抗击德意志第三帝国时,美国政府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公关运动,以清理美国这一新盟国的形象,使其符合自由主义理念。苏联此时已被描绘成最民主的国家(proto-democracy),斯大林也成了”约瑟夫大叔“(Uncle Joe)。
【注:关于这一主题的重要作品有:Ido Ore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Changing U.S. Perceptions of Imperial Germa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No.2(Fall 1995),pp 147-184。 John L.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Chap.2。英国决策者也曾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努力清除俄国形象的讨论。
本书的构想
第二章阐明了作者的理论即国家为什么争夺权力和追求霸权。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里,作者给权力下了定义,并解释如何度量权力。这主要是为检验作者的理论做铺垫。不弄懂什么是权力以及国家为了极大地占有世界权力所采用的不同策略,就无从确定国家是否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旨意行事。作者首先对潜在的权力与实际的军事实力进行了区别,然后指出国家对这两类权力都非常在意。第三章集中讨论潜在权力,主要包括一国的人口规模及财富数量。第四章讨论军事实力。这一章很长,因为作者探讨的是”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和”水域的阻遏力量“这两个既新颖有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
第五章主要探讨大国为获取和维持权力所运用的策略。用较大的篇幅讨论战争对获取权力的实效性。同时,作者还重要讨论了建立均势和推卸责任等主题,这是国家面对那些想打破均势的对手的威胁时所采用的主要策略。
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作者对历史记录进行考证,看是否存在支持本理论的证据。作者特别对西元1072-1990年之间的大国行为作了比较,并检查这些行为是否符合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预测。
在第八章中,作者提出了一个简单理论,解释大国何时建立均势以及何时选择推卸策略,然后运用历史记录检验该理论。第九章讨论战争的诱因。在这一章里,作者也提出了一个理论,然后以实证记录检验它。
第十章研究中国崛起。中国崛起是西元21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而作者要讨论这个最重要问题里最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所以这一章将用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预测崛起的中国会怎样面对其他亚洲国家和美国。而预测的结果并不乐观,中美两国安全竞争将愈演愈烈,周边国家大多会联合美国制衡中国。而且虽然很多人预测中国不会打仗,作者却认为两国很可能爆发战争。
第二章 无政府状态与权力竞争
大国总是寻找机会攫取超出其对手的权力,最终目标是获得霸权。除非存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占有绝对优势的国家,这种观点不允许维持现状国家(Status quo powers)的存在,相反,体系中到处是心怀修正主义(Revisionist)意图的大国。
大国谋求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
国家为什么追逐权力
国际体系鼓励国家寻找机会最大化地夺取权力。
基本命题
第一个命题是,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
第二个命题是,大国本身具备某些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为其彼此伤害甚至摧毁提供必要的资本。
第三个命题是,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
第四个命题是,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
第五个命题是,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
求生存本身是一个绝对无害的目标。不过,当五个命题同时具备时,他们就为大国萌发并采取针对他国的进攻行为创造了强大动力,尤其可能出现三种总的行为模式:畏惧(fear)、自助(self-help)和权力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
国家行为
安全困境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用来增加自己安全的测度标准常常会减少他国的安全。……即在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的最佳生存之道是利用其他国家,牺牲他国之利,为自己获取权力。最后的防御就是一种有效的进攻。由于这一信息被普遍认同,因此,无休止的安全竞争连绵不断。不幸的是,只要国家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就几乎不可能采取任何措施改善安全困境。
国家是追求权力的最大化者就等于说它们在乎的是相对权力而不是绝对权力。……权力不是达到目标(生存)的手段,而是目标之本身。
估算侵略
大国采取进攻行动之前,会仔细考虑均势以及其他国家对它们行动的反应。它们将估算进攻的代价、危险与可能的利益之间的得失。倘若利益不足以抵消危险,它们会按兵不动,等待更有力的时机。国家从来不会发动不可能提高他们总体地位的军备竞赛。 ……一国必须知道它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制度。
不过,大国也不时会出现误算,因为它们总是根据不完整的信息作出重要决定。国家对它们面对的任何形势几乎都没有完整的信息。这一难题有两个方面。潜在的对手有虚报它们自己的实力和弱点、隐藏真实目标的动机。试举一例,一个较弱国家试图阻止一个较强国家的进攻,前者可能夸大它的实力,以打消潜在侵略者的进攻念头。另一方面,一个打算采取侵略行动的国家可能突出它的和平目的,而夸大自己的军事弱点,以使潜在的受害者疏于建立他的军备,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也许没有哪一国的领导人比阿道夫·希特勒更会玩弄这种伎俩了。
【注:剩下的内容核心就是战就示敌以弱,不打就示敌以强。】
然而,即使假情报不是问题,大国也常常无法肯定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将如何表现。譬如,有时,很难事先确定新式武器和未经战争洗礼的战斗部队如何在敌人的火力面前发挥作用。和平时期的军事演习和战争游戏虽然有益,但是无法准确表现实战中可能发生的一切。打仗是一项复杂的赌博,常常难以预料结果。
有时,大国也既吃不准盟国的想法,也无法确定对手的意志。……
概言之,历史记载表明,进攻有时会成功,有时不会成功。关键在于,最大化地觊觎权力的国家要决定何时出手,何时收场。
霸权的极限
霸权是指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统治体系中所有其他国家。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备能承受起与之进行重大战争的资本。实质上,霸主是体系中唯一的大国。一个只比体系中其他国家更强大的国家不算霸主,因为严格地说,它还面对其他大国。
除非一国可能获得明显的核优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为全球霸主。统治世界的主要障碍在于,国家要跨越世界海洋到大国对手的领土上谋取权力非常困难。
大国能得到的最好结果是成为地区霸主,并可能控制在陆地上与之毗邻或易于到达的另一地区。
取得地区霸权的国家,常常试图阻止其他地区的大国续写它们的辉煌。换句话说,地区霸主不需要与之匹敌的对手。
此外,如果两个大国中冒出一个霸主,那么那一地区的其他大国本身可能牵制它,使远处的霸主安然无恙。当然,假如本地区大国不能完成这一使命,远方的霸主可能恰当的措施应对这一威胁国。
总之,任何大国的理想局面是成为世界唯一的地区霸主。那一国家将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它可以尽情地保护现有的权力分配。今天的美国就处于这种令人垂涎的位置,它支配着西半球,而且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没有霸主。但如果一个地区霸主面对一个可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那么它就不再是维持现状的国家。无疑,它一定会竭尽全力削弱甚至消灭他的远方对手。当然,两个地区霸主都会受到那一逻辑的驱使,它们之间必然发生剧烈的安全竞争。
权力与畏惧
这种逻辑一目了然:感到恐惧的国家特别卖命地寻找提高自己安全的出路,它倾向于用危险的政策达到那一目的。因而,弄懂是什么引起国家彼此或多或少地畏惧对方非常重要。
大国间的彼此畏惧来自于这一事实:它们总是具备一定用来抗击彼此的进攻性军事能力,而且任何国家都永远无法肯定其他国家不打算用这一能力来反对自己。此外,由于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运作,万一另一大国进攻它们,没有任何守夜人为它们提供帮助。虽然无政府状态和对其他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造成国家间无法消减的畏惧程度,导致追求权力最大化的行为,但是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有时恐惧程度要高于其他时候。原因在于无政府状态和辨别国家意图的困难是生活中常有的事实,常量是不可能解释变化的。然而,国家威胁彼此的能力因情况不同而各有区别,而且它是驱使恐惧程度或高或低的关键因素。特别是,一国获得的权力越多, 它令对手产生的恐惧就越深。
对于权力怎样引起恐惧的讨论,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权力。区别潜在的权力与实际的权力很重要。一国的潜在权力建立在它的人口数量和财富水平上。这两种资源是军事能力的主要支柱。拥有大量人口的富裕对手通常能建立令人胆寒的武装部队。一国的实际权力主要体现在它的陆军和直接支持它的空军及海军力量上。陆军是军事力量的核心成分,因为它是征服和控制领土(在一个以领土国家为特征的世界里极为重要的目标)的主要工具。简言之,即使在核时代,军事能力的核心成分也是陆上能力。
权力因素在三个主要方面影响恐惧的程度。第一,一个拥有能经受核打击并实施报复的核对手与它不具有核武器时相比,前一种情况造成彼此恐惧的程度要小一些。
第二,当大国被巨大的水体分隔时,它们常常不具有相互攻击的强大进攻能力,不管其军队的相对规模多大。
第三,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也会极大地影响恐惧的程度。关键的问题在于,大国间的权力是否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平衡分配,或是否存在极大的权力不对称性。产生最大恐惧的权力结构是多极体系,它包含一个潜在的霸主,作者称之为“不平衡多极”(unbalanced multipolarity)。
一个潜在的霸主不仅仅是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它是个具有巨大实际军事能力和很大潜力的大国,很可能支配和控制它所在地区的所有大国。一个潜在的霸主不一定立即拥有攻击它所有对手的资本,但必须具备击败单个对手的可观前途,并有逐个击败其中一些敌手的大好前景。其核心关系在于体系中的潜在霸主与次强国之间的权力鸿沟——它们之间一定存在显著的差距。要成为潜在的霸主,一个国家在本地区所有国家中不仅必须——以相当的差距——拥有最大的潜在权力,而且还要拥有最庞大的军队。
两极体系是最不容易引起大国彼此恐惧的权力结构,尽管这一恐惧并非微不足道。两极下的恐惧并非剧烈,原因在于,该体系中,两个大国常常保持大致的均势。不存在潜在霸主的多极体系,作者称之为"平衡多极“(balanced multipolarity),这种体系中的成员之间仍可能存在权力的不对称性,尽管这些不对称性不像体系中出现潜在霸主时那样明显。因此,平衡的多极可能比不平衡的多极体系产生的恐惧要少,但比两极体系引起的恐惧要多。
关于大国间恐惧的程度如何随权力分配的变化而改变,而不是随国家对每一方意图的估测而变化的讨论,引出了一个相关的问题。当一国考察它的环境,以决定哪些国家对自己构成威胁时,它主要关注潜在对手的进攻能力,而不是它们的意图。前面已经强调,意图是根本无法得知的,所以,为生存担心的国家必须对其对手的意图作最坏的假设。而力量却不一样,它不但可以被度量,而且能够决定一个对手是否为严重的威胁。总之,大国针对能力而非意图建立均势。
显然,大国抗衡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因为那种进攻性军事能力是它们生存的有形威胁。然而,大国对于对手控制多少无形权力也非常关注,因为人口众多的富裕国家通常能够而且事实上也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因而,大国常常需要提防拥有大量人口、经济增长快速的国家,即使这些国家还未把它们的财富转化为军事能力。
国家目标的层级
按照作者的理论,生存是大国的首选目标。但是,在实际中,国家也追求非安全目标。
只要必要的行为与均势逻辑不相冲突,国家就可以追求这些目标,而且常常如此。确实,追求这些非安全目标有时补充了对权力的猎取。
有时,追求非安全目标对均势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人权干涉常常属于这种情况。因为它们往往是小规模的行动,代价很小,也不会减损一个大国的生存前景。无论好坏,国家很少愿意以流血耗财的方式,保护外国人免受虐待甚至大清洗。
然后,有时,追求非安全目标与均势逻辑相抵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常常按现实主义的旨意行事。比如说,尽管美国承诺在全球传播民主,但在冷战中,美国却推翻一些民选的政府,扶植独裁政权,因为美国决策者认为这些行动有助于遏制苏联。……总之,当大国面对严重威胁时,一旦需要寻找联盟伙伴,它们很少顾及意识形态。
当安全与财富这两个目标相冲突时,前者重于后者,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言,”防御比财富重要得多“。【注:下面举了英国出台《航海法案》来打击荷兰的例子来说上述道理。】
创造世界秩序
【注:第一段提到的是美国领导人关于建立美好世界秩序开出了大量的空头支票。】
尽管这样说,大国不会为促进世界秩序而一同合作来促进世界秩序。相反,每一个国家都力求最大量地占有世界权力,这很可能与创造和维持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的目标相冲突。这并不是说大国从不想阻止战争与维持和平。相反,它们竭尽全力阻止使自己可能成为牺牲品的战争。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行为主要受狭隘地计较相对权力地动机所驱使,而不是为了创设一种独立于一国自身利益地世界秩序而承担义务。
无论何时,某种国际秩序的出现,大体上都是体系中大国自私行为的副产品。换句话说,体系的构造是大国安全竞争的无意识结果,而不是国家采取集体行动构建和平的结局。
诚然,正如冷战时的情况,大国对抗有时会产生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然而,大国将继续寻找机会,增加其分得的世界权力,一旦出现有利形势,它们会站出来打破那一稳定的秩序。……当然,权力丧失已成定局的国家将起来抵御侵略,维持现存的秩序。但它们的动机是自私的,是出于均势逻辑考虑,而不是出于某种对世界和平的义务。
有两种原因可以解释大国不可能为了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承担义务。首先,国家不可能为增进和平的一般性规则达成协议。……《凡尔赛条约》在改进欧洲的稳定问题上无功而返也就不奇怪了。
其次,大国不可能置权力考虑于不顾,而着手增进国家和平,因为它们无法肯定它们的努力能否成功。倘若努力失败,他们必将为忽视均势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一旦侵略者来到家门口,它们再拨打911,是得不到回应的。很少有国家会冒这种风险。因此,这种谨慎态度要求它们必须按现实主义逻辑行事。这些理由告诉我们,呼吁国家摒弃狭隘的均势考虑而按国际共同体的更广泛利益行事的集体安全计划,不可避免地要夭折。
国家间的合作
国家能够合作,虽然有时合作难以实现,而且总是难以持久。两类因素制约了合作:对相对收益的顾虑和对欺诈的提防。从根本上而言,大国处在一个竞争的世界中,在这里,它们至少把彼此看成潜在的敌人,而且它们希望以牺牲对手为代价获取权力。
任何两个试图合作的国家,都必须考虑在它们之间如何分配收益。它们可能按照绝对或相对收益的标准来考虑分配问题。在绝对收益情况下,每一方关心的是自己最大化地占有利益,毫不在乎他国在交易中的得失。只有当他国行为影响到自己对权力的最大化占有时,各方才会在乎对方。而另一方面,在相对收益的情况下,每一方不但考虑自己的个体收益,而且关心己方是否获得了较他方更多的收益。
由于大国非常注重均势,因此,当它们考虑与其他方合作时,集中考虑相对收益问题。每个国家无疑想使自己的绝对收益最大化,但对一个国家来说,更重要的是确保它在任何协议中都不会亏待自己,而且做得更好。然后,当国家把着眼点转向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时,合作就变得更为困难了。这是因为,关心绝对收益的国家必须保证,一旦馅饼做大后,它们至少能得到增加部分的份额,而关注相对收益的国家必须对馅饼的分配特别留心,这就使合作的努力复杂化了。
对欺诈的担心也会妨碍合作。大国常常不愿意参加合作协议,担心其他方会在协议中耍欺骗手段,以获得可观的优势。这一担心在军事方面尤其敏感,并会引起”背信弃义的特殊危险“,因为在均势情况下,军事装备的属性是快速变化的。这种变化可以为国家创造一个机会,让其运用欺骗方式,使它的受害者遭受决定性的失败。
尽管合作存在诸如此类的障碍,但现实主义世界中的大国确实也存在合作。均势逻辑常常促使大国结成联盟,联合反对共同的敌人。……对手和盟友都会合作。毕竟,只要这些交易能大体反映权力的分配和消除对欺诈的担心,就可以成交。冷战期间,超级大国签订的各式军备控制协定就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它的底线是,合作发生在一个以竞争为内核的世界中,在这里,国家具有利用他国的强烈动机。……合作的多少不可能消除安全竞争的主导逻辑。只要国家体系仍处于无政府状态,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和平,世界总是充满安全竞争。
结论
总之,作者的观点是,是国际体系结构而不是国家个体的属性促使它们以进攻的方式思考、行动和追求霸权。摩根索认为,国家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侵略行为,是因为它们具有一种内在的权力意志。作者不接受这种观点。相反,作者认为,大国行为背后的首要动机是生存。然而,在无政府状态下,对生存的渴望促使国家实施侵略行为。因此,作者的理论从不以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为依据,进而把它们划分成侵略性强或弱的国家。进攻性现实主义只是提出了关于大国少数假设, 这些假设同样适用于所有大国。除了在每一国家控制多少权力问题上的差异上,该理论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
注释:
如果一国获得霸权,该体系就不再是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了等级体系。进攻性现实主义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它对等级制度下的政治几乎没有涉及。但如后所论,任何国家要想成为全球霸主是绝对不可能的,尽管地区霸权有可能实现。因此,除了关注被一霸主统治的某一地区内所发生的一切,现实主义也可能对可见的将来的世界政治提供重要的参考。
虽然大国总是怀有侵略意图,但它们并不总是侵略者,主要因为它们有时不具备采取侵略行为的能力。作者在全书中都使用”侵略者“一词,是表示大国具有按自己意图行事的物质能力。
第三章 财富和权力
作者认为权力以国家拥有的某些物质能力为基础。
国家有两种权力: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潜在权力指的是,用来构筑军事权力的社会经济要素。它主要以一国的财富和总的人口规模为基础。大国需要资金、技术和人员来建设军队并实施战争,一个国家的潜在权力是指它与对手竞争时所能调用的潜能总和。
然而,在国际政治中,一国的有效权力是指它的军事力量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以及与对手的军事实力对比的情况。
军事权力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的陆军规模、实力以及与之相配的海空力量。即使在一个核世界里,陆军也是军事权力的核心成分。单独的海军和战略空军力量不能用于抢占领土,也无法用来胁迫他国作出领土让步。虽然它们有助于赢得一次成功的战役,但大国间的战争主要通过地面站获得胜利。因此,最强大的国家是指那些具有非常庞大的地面部队的国家。
尽管军事权力具有以上优势,但国家也特别在乎潜在权力,因为充足的财富和众多的人口是建立庞大军队的先决条件。……这些事例说明,国家既关注潜在权力均势,也在乎军事权力均势。
下一节讨论为什么从物质能力而不是从结果这一学者青睐的方法来给权力下定义更具意义。作者也会解释,为什么均势不能很好地保证军事胜利。结下的三节着重探讨潜在权力。首先,作者讨论了财富对建立强大军队的重要性,然后描述作者用来获取潜在权力的财富标准。其次,作者运用一些历史范例证明,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大国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体系中主要行为体之间财富分配的变化。第三,作者解释了为什么财富和军事权力虽然紧密相连,但并不等同。作者还说明了,财富不能被用来作为军事实力的测度标准。最后,作者认为,有必要为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分别设立一个参照体。
权力的物质基础
根据作者对权力的定义,权力不过是国家所能获得的特殊资产或物质资源。但是,其他人从国家间的互动结果来定义权力。他们认为,权力的全部含义是指对其他国家的控制和影响,是指一国迫使另一国去做某事。
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如何部署它的军队对付敌对国家。这可能是非物质因素中最重要的要素。有时,聪明的战略使弱于或不强于战场对手的国家取得胜利。
由三个原因表面权力并不等同于结果。首先,当强调结果时,就不可能在冲突之前评估均势,因为只有我们看到哪一方赢得胜利后,均势才能被确定。其次,这种方法有时导致虚假的结论。……第三,国家关系中最有趣的方面之一是,权力作为一个手段如何影响政治结局这一目的。
人口与财富:军事权力的原动力
实际上,人口众多并不能确保产生大量财富,但巨大的财富需要一个巨大的人口规模。因此,只有财富本身才能被用作衡量潜在权力的尺度。
财富的概念有多种意义,可以用不同方式度量。但作者认为有必要选定一个体现一国潜在权力的财富指标。特别是,作者必须注重一国的可支配财富(mobilizable wealth)和它的技术发展水平。”可支配财富“指的是,一国可随时调动建立军事力量的经济资源。它比财富总量更重要,因为重要的不是一国如何富裕,而是它有多少财富可资利用。同时,拥有能生产最新和最先进技术的产业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总是能转化成最先进的军备。
军事权力的经济基础
西元19世纪,法国和德国(1870年前为普鲁士)之间均势的深刻变化以及1800-2000年间俄国均势地位的变化,充分说明了财富是决定权力的关键因素。
然而,经济实力并不总是军事能力的很好指标。
潜在权力与军事权力之间的鸿沟
权力本身并非总能反映财富的梯级,原因有三。第一,国家把其财富的不同部分转化为军事实力;第二,财富转化为军事实力的效率因情况不同而各异,有时对均势产生重要的影响;第三,大国组建各式各样的军事力量,而且那些选择也关系到对军事平衡的估价。
逐渐缩小的汇报
如果发动军备竞赛不可能使发起者处于更有利的战略位置,它就会静观其变,等待更有利的形势。
尽管所有的大国都是富裕国家,但并非所有富裕国家都是大国。
不同水平的效率
把经济实力的分配与军事能力的分配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因为国家把财富转化为军事权力的效率各不相同。有时,大国对手之间存在很大的效率差距,这对均势产生极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的生死之战就说明了这一点。
军事力量的不同种类
财富不是军事能力的可靠参照体还有最后一个原因,那就是国家可以借用不同种类的军事权力,而且它们怎样建立武装部队对均势也具有影响。这一问题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这里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一个拥有庞大军队的国家是否具备可观的权力投送能力。然而,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把相同比例的防御资金用于军事,也并非所有的军队都具有相同的权力投送能力。
第四章 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
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是一国军事力量的产物。但是,大国可以获取不同种类的战斗力量,每一种力量的多少对均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章考察国家选择的四类军事力量——独立的海军力量、战略空中力量、地面力量和核武器——以便相互权衡,提出权力的有用度量模式。
在下面的讨论中,作者将提出两个观点。第一,地面力量是当今世界军事力量的主导形式。
第二,巨大的水体极大地影响地面力量的投送能力。
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及其他著述中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独立的海军力量是至高无上的。西元1921年,意大利将军吉乌里奥·杜黑(Giulio Douhet)则在他的名著《制空权》中提到战略空中力量的统治地位。这些著作至今仍是世界各地参谋学院的流行读物。作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地面力量才是决定性的军事手段。战争靠庞大的陆军而不是海上的舰队和空中的飞机取得胜利。最强大的权力是拥有最强大陆军的国家。
征服与胁迫
在战争中,陆军极为重要,因为它们是征服和占据领土的主要军事工具,而在领土国家的世界里,领土是最高的政治目标。
虽然海军封锁和战略轰炸机本身不能取得胜利,但有时它们通过摧毁经济和破坏敌人的战争机器来协助陆军赢得胜利。然而,即便有这种超乎限度的能力,海空力量也常常不过是起一种辅助作用。
地面力量主导其他形式的军事力量还有另一种原因:只有陆军才能快捷地击败对手。下文将谈到,在大国战争中,封锁和战略轰炸不可能产生快速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它们主要有利于打消磨站。但是,除非国家认为能速战速决,它们一般很少开战。事实上,如果国家预见到可能会发生一场长期的冲突,那么,它就会极力避免战争的爆发。因而,一国大国的陆军是它发动侵略的主要工具。换言之,一国的攻击能力主要来自陆军。
独立海上力量的局限性
依靠向敌国投送力量的海军必须首先获得”制海权“,这是海军的根本使命。制海权意味着控制海洋表面纵横交错的航线,以便一国的商业和军事船只能自由航行。一支海军控制海洋,并不需要它一直控制所有海域,但是,无论何时,只要它需要,就必须得从战略上控制部分重要海域,并阻止敌人获得同样的能力。制海权可以通过在战争中摧毁敌人的海军、封锁它们的港口或使对方无法使用关键的海上航线等方式获得。
一支控制海洋的海军也许可以在它控制的区域自由活动,但它仍需找到向对手领土投送力量的途径。制海权本身不具有这一能力。海军能执行三种力量投送任务,在这三种任务中,它可以直接支持陆军而不是采取独立行动。
- 两栖进攻
- 两栖登陆
- 军队运送
国家通常使用海军力量实施封锁,因为它可以阻止远洋贸易到达目的国。……潜艇也可以用来截断对手的海上贸易。……控制一片大陆及其主要港口的国家,可以阻止该大陆上的国家与位居他处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并因此封锁外部国家。
封锁的历史
但有封锁不可能迫使敌人投降,封锁只能增加被封锁对象的维稳成本。
为什么封锁会失败
即使当封锁完全截断了目的国所有的海上贸易,它的效果也常常是有限的,原因有二。第一,大国有打破封锁的方法,比如再生利用、储存和替代等。在两次世界大战前,英国都严重依赖粮食进口,而德国在这两场战争中的封锁,旨在使英国遭受饥荒之苦,使其降服。然而,英国大量增加它的粮食生产,化解了对其生存的威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德国的橡胶供应被断绝后,它就生产人造替代品。另外,大国可以征服和盘剥邻国,特别是铁路出现后尤其如此。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完全剥夺了欧洲大陆的资源,大大降低了盟国的封锁效果。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特别善于调节和合理配置经济,以反击战时封锁。
第二,现代国家的人们能消化很大的苦痛,而不会起而反对政府。历史记录中没有一个事例可以证明,以封锁或战略轰炸惩罚敌国的平民,会引起过公众对所在国政府的广泛抗议。如果有的话,也似乎是”惩罚引起更多公众对进攻者而不是本国政府的愤怒“。以二战中的日本为例,不但它的经济受到了美国封锁的破坏,而且它还遭到战略轰炸,城市满目疮痍,成千上万市民被炸死。然而,日本民众忍辱负重地承受了美国给予的毁灭性惩罚,他们并没有给自己的政府施加压力,促其投降。
【注:这块翻译得不好,日本民众不是活该吗?能叫忍辱负重吗?倭国民众并不无辜,原子弹下也没有冤魂,倭国民众比倭国上层更加该死!二二八事件也和这种大轰炸有关,当然这是后话了。】
最后,统治精英们很少会作出放弃战争的决定,因为他们的民众正受野蛮的摧残。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平民受到的惩罚越多,政府就越难停战。这种论点似乎违背直觉,它的基础是,惨重的失败极大地增加了这一可能性,即战争之后,人们将报复把他们带向毁灭的领导者。因此,那些领导人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不顾人们遭受的苦难,决心战斗到底,希望能渡过难关,走向胜利,保全自己。
战略空中力量的限度
在战争中,国家如何部署它们的空军和海军同样重要。但是,在海军把力量投送到敌国之前,它们必须获得制海权;而空军在轰炸敌人的地面部队或进攻对手的本土前,必须获得制空权,或获得通常所说的空中优势。如果空中力量不能控制天空,它的打击力量很可能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是难以有效地向敌人投送力量。
一旦空军控制了天空,它就可以执行三项力量投送使命,支持在地面作战的陆军部队。就低空援助(close air support)的作用而言,空军力量飞掠战场上空,为在下方采取行动的友好的地面部队提供直接的战术支援。空军的主要目的是从空中歼灭敌人,实际上是充当”飞翔的炮兵“(flying artillery)。这一使命要求空中与地面力量的密切配合。阻断(interdiction)指的是空军打击敌人陆军的后方地区,主要是为了破坏并延缓敌人对前线的供给和运送部队。打击目标可能包括补给站、预备部队、远程炮兵以及联系敌人后方与前线的交通线等。空军同时也提供空运,向战区或在战场内运送部队和提供补给。当然,这些使命只是加强陆军的能力。
然而,空军也可以用战略轰炸单独向对手实施武力,它可以直接打击敌人的本土,而无须考虑战场上的战况。……战略轰炸如同封锁一样,不可能取得快速和轻而易举的胜利。
在过去的十年里,一些空军倡导者认为,战略轰炸可以通过处决敌人政治领导人的方式来确保战争的胜利。尤其是,战略轰炸机可以用来谋杀敌国的政治领导人,或攻击领导层的通讯设施和安全部队,把他们与国民隔离开来。这种观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阵营中的温和派将发动政变,举行和谈。主张处决敌人领导人的观点认为,把政治领导者与其军事力量隔离开来,使他无法控制和指挥军队是可以实现的。
然而,当评估大国之间的军事力量平衡时,拥有轰炸小国和弱国的能力是无足轻重的。最关键的是,大国在彼此对抗时可能使用的军事装备,这里不再包括战略轰炸。
战略轰炸的历史
这14个战例应参考前面关于封锁的两个问题来评估。第一,有无证据证明,单有战略轰炸就能胁迫敌人投降吗?第二,战略轰炸能为地面陆军取得胜利起到很大作用吗?战略轰炸对战争的最终结局是否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与地面力量的效果大致相等还是相距甚远?
轰炸大国
轰炸小国
单纯的战略轰炸不能胁迫敌人投降。
战略轰炸几乎不可能削弱敌人的陆军,因此,它也就不可能为地面战争的成功作出重大贡献。二战期间,独立的空中力量有时确实帮助过大国赢得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但是,它在那些胜利中只起一种辅助作用。在核时代,大国只运用这一威慑工具打击次大国,而不是彼此攻击。不过,即使用来打击较弱的国家,战略轰炸的效果也一直与打击其他大国时差不多。一句话, 它很难把对手炸向投降之路。
战略轰炸行动为什么失败
战略轰炸不能奏效和封锁常常不能胁迫对手的原因是一样的:平民能忍受巨大的痛苦和掠夺,而不致起来反对他们的政府。政治学家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对空中惩罚与平民造反的历史证据作了总结:”在75年多的时间里,空中力量的记录无非是,试图利用进攻或威胁要攻击大量平民等方式,改变国家的行为。从这些战役里得出的无可争议的结论是,空中打击不会引起国人反对他们的政府……事实上,在过去30多场重大的战略轰炸行动中,空中力量从未迫使群众走向街头要求任何东西。“在这,现代工业经济不是容易摧毁的脆弱结构,即使大规模的空中攻击也难以奏效。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解释就是,大国的经济有许多经得起毁灭的余地。用这一战略来进攻次大国就更没有多少意义了,因为它们的工业基础都很小。
【注:这确实扭转了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暗杀政治领导人的行动是一个简单的战略。不过,杜达耶夫的事例表明,战时要找到并剿杀对手的政治领导人尤其困难。但即使剿杀行动得手,对手继任领导人的政见也不会与其前任有多大差异。
另外,像希特勒一样的邪恶领导人拥有广泛的民众支持:有时,他们不仅代表他们国家的观点,而且民族主义常常会在政治领导者和其人民之间培育出紧密的纽带,特别是在战时,当国家面临一个强大的外来威胁时尤其如此。
提倡把政治领导人与其广大人民隔离开来的战略也是不切实际的。领导者有许多渠道与其人民保持联系,实际上,空中力量不可能将其一举摧毁,并长时间地关闭这些渠道。……最后,战争期间,促使敌国内部发生一场能产生友好领导者的政变,是一项特别困难的任务。
同样,把一个领导人与他的军事力量隔绝开来也是不切实际的。在这一战略中,成功的关键在于切断联系战场与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交通或通讯线。不过,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何这一战略注定会失败。领导者拥有多种渠道与其军队和人民保持联系,轰炸机不可能同时将它们封堵,更不可能让其长时间保持缄默。另外,对这一难题感到担心的政治领导人,会事先将权力移交给军方指挥官,以防交通线被切断。例如,冷战期间,由于担心核武器可能伤害领导人,两个超级大国都为这种不测作了安排。
陆军的决定性影响
水域的阻遏力量
为什么水域是陆军的屏障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侵略一方应在其登陆点上空拥有明显的空中优势,以便它的空军能提供就近的空中支援,阻止敌人增援海滩。
但如果所有这些条件都不具备,而且防御大国能把其绝大部分军事力量都用来反击两栖力量,那么毫无疑问,陆基部队会给海上入侵者以毁灭性还击。
两栖进攻的历史
大陆大国对岛屿大国
核武器与均势
作者的观点是,倘若单一的大国获得核优势,它将成为霸主,这无疑意味着再也没有大国对手与之进行安全竞争。在这种世界中,常规力量对均势不再产生影响。但是,倘若两个或更多大国拥有确保自己生存的核报复能力,那么它们之间的安全竞争将会持续,地面力量仍然是军事力量的关键成分。然而,毫无疑问,核武器的问世使得国家在运用任何形式的军事力量攻击对手时,都更为小心谨慎。
核优势
国家获得核优势的最好办法是用核武器武装自己,并确保其他国家不拥有核武器。一个拥有核垄断的国家就如同这一概念所言,一旦它发射核武器,无须担心任何种类的报复。
在拥有两个或更多国家装备核武器的世界里,如果一国能发展压制对手核武器的能力,该国就可能拥有核优势。为了获得这种优势,大国要么获得”绝对的第一次打击“能力,压制对手的核武库,要么发展保护自己免受对手核打击的能力。但是,核优势的获得,并不仅仅是因为一国比另一国拥有多得多的核武器。一国只要有足够的较小的核武库能抵挡第一次打击,并能对拥有更大核武库的国家实施大规模惩罚,那么这种不对称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没有意义。
任何国家只要获得了超过对手的核优势,就有效地成为该体系中的唯一大国,因为该国的力量优势将非常巨大。核霸权可以威胁使用使用强有力的武库,给对手造成巨大破坏,有效地消灭它们运行的政治实体。而如果潜在的受害者没有能力进行这种反击,这种核威胁就具有了可信度。核霸权能把它的致命武器用于军事目的,如集中打击敌人的地面部队、空军基地、海军舰只,或敌人指挥和控制系统的关键目标。再者,被打击国没有匹配的能力,因此给了核霸权一个决定性优势,根本无须考虑常规力量的均势问题。
每一个大国都想获得核优势,但它们不可能经常如愿,就算确实出现此种局面,也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没有核武器的对手肯定会想方设法建立自己的核武库,一旦它们如愿以偿,那么大国就很难(虽然不是不能)通过保护自己免受核打击的方式重建核优势。
冷战中,美苏双方被迫接受这一事实:不管它如何部署自己的核力量,另一方仍有确保生存的核报复力量,给进攻方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德克萨斯均衡“(Texas standoff)被称作”相互确保摧毁“(MAD),因为无论哪一方挑起核战争,很可能双方都会被摧毁。不管哪一个国家如何渴望超越”相互确保摧毁“定则,建立核优势,核战争都不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爆发。
在”相互确保摧毁"世界里的军事力量
一个”相互确保摧毁"的世界在核水平上是高度稳定的,因为任何大国都没有动机发动一场无法取胜的核战争;事实上,这种战争可能导致它的社会走向瘫痪。因此,问题依然存在:此类恐怖平衡对核武器大国间的常规战争的前景有何影响?
【注:作者下面反驳了两种流派的观点。这里不赘述了。】
地面力量均势仍然是核时代军事力量的中心成分,尽管核武器肯定使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变得更小。
度量军事力量
度量地面力量均势有三个步骤。第一,必须估测对手军队的规模和素质。在和平时期和军事动员后,研究这些力量的实力很重要,因为国家通常保持小型的常备军,一旦预备役军队被动员执行任务,常备军可以迅速扩充规模。
主要考虑因素:士兵数目、士兵素质、武器数量、军备质量、这些士兵和武器如何为战争而组合
测量地面力量均势的第二个步骤是,把任何支援陆军的空中力量列入分析之中。我们得算出各方飞机的总数,重点考察能得到的数目和质量。同时,还必须考虑飞行员的效率以及每一方几下几方面的实力:(1)陆基防控体系;(2)侦察能力;(3)战争管理体系。
第三步,我们必须考虑陆军内在的力量投送能力,尤其关注巨大的水体是否限制陆军的进攻能力。
结论
陆军和支持它的海空力量是当今世界最高的军事力量形式。然而,庞大的水体极大地限制了陆军投送力量的能力。核武器大大降低了大国陆军冲突的可能性。不过,即便在核世界里,地面力量仍然是至高无上的。
由于海洋限制了军队投送力量的能力,而且核武器降低了大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因此,最和平的世界可能是,所有大国皆为岛屿国家,并拥有确保生存的核武库。
第五章 生存战略
我们考察一下大国如何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第一项任务是,列出国家在权力竞争中所追求地特殊目标。作者对国家目标的分析是以前述章节所讨论的权力为基础的。特别是,作者认为大国在它们所控制的地区内争夺霸权。由于巨大的水体增加了向对岸投送力量的困难,因此,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支配整个世界。大国也追求富裕,它们实际上比对手富足得多,因为其军事力量有一个经济基础。另外,大国渴望在它们所处地区内拥有最强大的地面部队,因为陆军和支援它的海空部队是军事力量的核心成分。最后大国寻求核优势,尽管这一目标很难达到。
第二项任务是,分析国家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改变均势,以及阻止其他国家作出不利于自己均势变化的不同战略。战争(War)是国家获取权力所采用的主要战略。讹诈(blackmail)是一个更具吸引力的选择,因为它依靠武力威胁而不是运用实际武力达到目的,因此成本较低。然而,讹诈往往难以得手,因为大国很可能在屈服于他国威胁之前就投入了战争。获得权力的另一种战略是诱捕(bait and bleed),即一国试图挑起对手间长期而昂贵的战争来削弱它们。不过,这一伎俩也难行通。该战略的一个更乐观的变数是坐观血腥厮杀(bloodletting),即一国采取某些措施,确保敌国所卷入的任何战争都是持久而致命的。
建立均势和推卸责任是大国用来阻止敌人颠覆均势的主要战略。通过建立均势,受威胁的国家本身必须参与遏制危险的对手。换句话说,它们愿意担负遏制和必要时抗击入侵者的重任。而采用推卸责任的战略,它们就可以设法让另一大国遏制入侵者,自己则冷眼旁观。受威胁的国家常常会采用推卸责任而不是均势战略,因为在战争爆发时,推卸责任者(buck-passer)可避免与侵略者打斗的代价。
绥靖(appeasement)和跟着强者走(bandwagoning)战略对应付侵略者不是特别有效。二者都要求向敌对国家出让权力,在一个无政府体系中,这预示着大麻烦来临了。就”跟着强者走“而言,受威胁的国家不会阻止侵略者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获取权力,而是与危险的敌人结盟,希望至少可以从战争中获得少量战利品。”绥靖“和”跟着强者走“都是无效而危险的战略,因为它们使均势朝不利于受威胁国家的方向变化,但作者还是要讨论一些特殊情况,因为在这里,一国向另一国让与权力是有意义的。
国家关系领域一个常见的观点认为,建立均势和跟着强者走是受威胁的国家所能选择的关键战略,大国总是要抗衡危险的对手。作者不同意这一说法。正如前面所强调的,跟着强者走不是现实世界中的有效选择,因为虽然跟着强者走的国家可以获得较多的绝对权力,但是危险的侵略者会取得更多权力。在现实世界中,实际的选择是建立均势和推卸责任。无论何时,受威胁的国家更愿意采用推卸责任而不是建立均势的战略。
最后,作者把其理论与现实主义的著名论断联系起来,即效仿敌对大国的成功实践是安全竞争的重要结果。作者认为其基本点是正确的,但是作者认为,这种观点狭义地定义了这种效仿行为,过于强调照搬进攻而非防御行为。另外,大国也提防革新,这常常意味着,它们会采用聪明地办法以牺牲对手为代价来获得权力。尽管本章考察了各种各样的国家战略,但是有三个中心点:战争是增加额外权力的主要战略,而建立均势和推卸责任是维持均势的主要战略。对于受威胁的国家如何选择建立均势和推卸责任的问题,将在第八章中加以分析,而第九章将研究国家何时会选择战争的问题。
行动中的国家目标
地区霸权
大国瞄准四个基本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它们追求地区霸权。
地区霸权如何阻止其他大国支配远处的地区,要取决于那些地区的均势。如果那些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均匀,它们之中就不存在潜在霸权,那么远处的霸权就可以安全地置身于那些地区的任何冲突之外,因为没有国家强大到可以征服所有其他国家。不过,即使另一地区出现霸权,远处霸权的首要选择也可能是袖手旁观,让当地大国遏制那一威胁。这就是绝妙的推卸责任战略在起作用,就像下面要讨论的,国家在面对一个危险敌人时,更愿选择推卸责任而不是建立均势。然而,倘若当地大国不能遏制那一威胁,那么远处的霸权就会进驻该地区,与之抗衡。虽然它的主要目标是遏制,但是远处的霸权同时也会伺机消除这一威胁,在那一地区重建大致的均势,以便它能打道回府。实质上,地区霸权在世界其他地区扮演平衡手角色,尽管它们更愿意充当最后关头的平衡手。
【注:简而言之就是老大应该拉拢老三遏制老二。《君主论》中也提到了这点。】
也许有人会问,一个在本地区独霸一方的国家,尤其是两个被大洋分割开来的竞争者,为何在乎另一地区是否存在霸权呢?毕竟,两个地区霸权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跨越水体攻击另一方。
然而,被大洋分隔的敌对霸权,仍然可以通过在对方的后院颠覆均势的方式来彼此威胁。特别是,一个地区霸权有朝一日可能会面对来自一个暴富国的本地挑战,后者无疑有一种与远处霸权联盟的强烈动机,以保卫自己免受临近霸权的攻击。同时,远方霸权与那一暴富国合作也有自己的原因。务必记住,有很多原因可解释为什么国家彼此试图占便宜。在这些情形下,水体的阻遏力量几乎不会影响远处霸权的权力投送能力,因为它无须跨过海洋发动两栖登陆,而是跨过水体,将军队和给养运到处于敌对霸权后院的盟友领土。摆渡部队比从海上入侵对手要容易得多,尽管远处得霸权仍要在海上自由行动。
使财富最大化
大国的第二个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财富。
还要指出的是, 大国特别把富裕的国家和朝富裕方向发展的国家看作严重威胁,不管它们是否拥有庞大的军事能力。毕竟,财富能很容易转化为军事能力。
同时,大国也想阻止对手控制世界上的财富生产地。
卓越的地面力量
大国的第三个目标是控制地面均势,因为那是它们最大限度地占有军事力量的最好方法。
核优势
大国的第四个目标是寻求超过其对手的核优势。
猎取权力的战略
战争
战争可能获利也可能赔本。
讹诈
国家可以用牺牲对手的方式为自己获取权力,而无须为之发生战争,使用强制和胁迫而不是实际的武力产生所期望的结果。倘若这种讹诈能起作用,那么它显然比战争更好,因为讹诈达到目的不以流血为代价。然而,讹诈不太可能导致重大的均势改变,主要原因在于,单独的威胁常常不足以迫使一个大国向另一大国对手作出重大让步。就定义而言,大国指的是它们彼此具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因此,它们不可能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向威胁投降。讹诈更可能发生在那些没有大国盟友的次大国身上。
诱捕
这一策略旨在造成两个对手投入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彼此耗尽能量,而投放诱饵者在一旁静观,完好无缺地保持军事力量。
坐观血腥厮杀
其目的是,确保其对手之间的战争变成一个耗尽它们力量的长期而代价高昂的冲突。这种战略不施放诱饵。对手独立地参加战争,而坐观者(bloodletter)只关心促使对手彼此消磨力量,自己则置身于战争之外。
制止侵略者的战略
大国不但寻求获取多于对手的权力,而且其目标是阻止对手以损害它们为代价获得权力。
建立均势
通过建立均势,一个大国直接承担组织侵略者颠覆均势的责任。其初期目标是阻止侵略,但如果该目标失败,建立均势的国家就将投入随后的战争。受威胁的国家可采取三个措施构筑均势工程。第一,它们可以通过外交渠道(和下文所说的行动)向侵略者发出清晰信号,表明它们坚定地履行均势原则,即使这意味着战争。均势维持者的照会中强调的是对抗,而不是安抚。实际上,均势维持者在沙地上画了一条线,警告侵略者不得越过它。
第二,受威胁的国家可以创建防御同盟,帮助它们遏制潜在的对手。这一外交应变常常被称作”外部均衡“(external balancing),只限于两极世界,因为这里没有潜在的的大国联盟伙伴,尽管与次大国结盟仍然是可能的。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和次大国结盟,因为它们是体系中的唯一大国。受威胁的国家把很高的赌注押在寻找联盟伙伴上,因为阻止侵略的代价由联盟分摊(战争爆发时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另外,募集盟国增加了对抗侵略者的火力,反过来又增加了威慑的作用。
尽管存在这些利益,外部均势还是有一个缺陷:它常常启动缓慢,而且效率很低。……把均势联盟快速集结起来并让它迅速起作用往往很困难,因为整合盟国或成员国需要时间,即使就需要做的达成了共识,也要假以时日。受威胁的国家经常在联盟成员如何分摊任务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毕竟,所有国家都是利己的行为体,都具有以最小的代价遏制侵略者的强烈动机。如下所述,这一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联盟成员国之间还有一种推卸责任的冲动。最后,联盟成员国之间很可能就哪个国家领导联盟的问题存在摩擦,当该联盟最终作为一个战略出现时就更是如此。
第三,受威胁的国家能调动它们自己额外的资源对抗侵略者。比如,增加防御开支和补召战斗人员。这种行为通常被称为”内部均衡“(internal balancing)。从这一术语本身看,它属于自助性质。但是,对于一个受威胁的国家能征召多少额外资源反对侵略者,常常有较大限制,因为大国通常已将其很大比例的资源用于防御。由于国家一心想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国家时刻都在有效地参与建立内部均势。不过,当面对一个侵略成性的对手时,大国会消除体系中的任何疏忽,寻找聪明的方法, 增加防御开支。
然而,并非所有的大国都会为了抵御侵略者而增加防御开支,也有一个例外情况。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离岸平衡手,当它们没有必要在一个重要的战略区域遏制一个潜在霸主时,往往会维持较小规模的军事力量。
推卸责任
推卸责任是受威胁的大国在建立均势时的主要选择。推卸责任者试图让另一国承担阻止或抗击侵略者的重任,自己则置身于外。推卸责任者深刻认识到,有必要阻止侵略者增加对世界权力的占有,但它必须指望某个其他受到侵略者威胁的国家能够完成这项繁重的任务。
受威胁的国家可采取四个措施实施推卸责任战略。第一,它们可以寻求与侵略者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至少不要刺激它,并希望后者把注意力集中在预先设计好的”责任承担者“(buck-catcher)身上。
第二,推卸责任者往往与预计的责任承担者保持冷淡关系,这不仅因为这种外交距离有助于与侵略者发展良好的关系,而且因为推卸责任者不想与责任承担者一块被拖进战争。推卸责任者的最终目标是避免与侵略者的战争。无怪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岁月里,法国与苏联的关系表现为低调的敌意。
第三,大国可以动员自己额外的资源,使推卸责任发挥作用。推卸责任似乎应该对防御开支采取松懈的做法,因为该战略的目标是让其他人遏制侵略。但是,除了上述所说的离岸平衡手这一例外情况,这一结论是错误的。姑且不看国家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这一事实,还有其他两个原因促使推卸责任者把自己装扮成令人生畏的目标,从而促使侵略者把注意力集中在预定的责任承担者身上。这里的逻辑很简单:一个受威胁的国家越强大,侵略者就越不可能进攻它。当然,前提是,在没有推卸责任者的帮助下,承担责任者必须仍有实力遏制侵略者。
出于预防不测的原因,推卸责任者也会建立庞大的军事力量。在具有两个或更多国家试图推卸责任的世界里,任何国家都不能肯定它不会承担责任并独自抗击侵略者。做好准备以防不测会更好些。例如,西元20世纪30年代,法国和苏联都无法保证自己不需要承担责任并单独抵抗纳粹德国。然而,即使一国成功地推卸了责任,也总是存在侵略者迅速而彻底地击败责任承担者后再进攻责任推卸者地可能性。因此,为了保险起见,一国可能会增加防御,以防推卸责任策略的失败。
第四,有时,推卸责任者允许甚至推动预期的责任承担者增加力量也是有意义的。这样,责任承担者会拥有更好的机会遏制侵略国家,并增加推卸责任者保持旁观的前景。
推卸责任战略的诱惑
推卸责任和把均势联盟组合在一起的做法,是两种对付侵略的截然不同的方法。不过,在均势联盟中还是有一种强烈的推卸责任或”搭便车“(free-ride)倾向,尽管推卸责任有一股强大的抵消力量,即毁坏联盟的危险。
推卸责任也具有攻击的成分,这使得该战略更具吸引力。特别是,当侵略者和责任承担者卷入一场长期而代价昂贵的战争时,均势有可能朝有利于责任推卸者的方向转移,然后,它处于支配战后世界的有利位置。
当一国面对不止一个危险对手并缺乏与之立即对抗的军事力量时,推卸责任也不失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选择。推卸责任有助于减少威胁。
然而,推卸责任并非绝对安全的战略。它的主要缺陷在于,责任承担者可能无法遏制侵略者,使推卸责任者处于危险的战略地位。
另外,推卸责任者允许责任承担者增加力量的情况下,也存在一种危险,那就是承担责任者最终会变得相当强大,从而威胁均势局面,就像西元1870年德国统一后所发生的一切。
虽然这些潜在的问题值得关注,但是它们最终不会减弱推卸责任战略的吸引力。大国并不认为它会导致失败。相反,它们期望从这一战略成功。否则,它们会避开推卸责任,而与体系中其他受到威胁的国家组成均势联盟。
很明显,推卸责任有时产生和诱捕战略一样的结果。特别是当推卸责任导致战争时,推卸责任者会像诱饵投放者一样充当旁观者,提高它的相对实力地位,而让它的主要对手彼此消耗。另外,如果战争中的一方赢得迅速而彻底的胜利,那么这两种战略会以相同的方式失败。不过,这两种战略有一个重要区别:推卸责任主要是一种威慑战略,不以战争为前提,而诱捕的目的在于挑起战争。
【注:现在的俄乌战争就是俄国不能速通被耗在乌克兰。】
规避战略
在乎自己生存的大国应该既不能对敌人采取绥靖政策,也不能对它们采用跟着强者走的战略。
跟着强者走战略违背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国家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相对权力,因此,它很少被大国采用,因为从概念上讲,这些国家具有与其他大国进行大战的财力,更何况,它们必然有对抗和战争的动机。跟着强者走战略主要被那些无法独自与敌对大国对垒的次大国所采用。
绥靖指的是受威胁的国家对侵略者让步,使均势朝受益一方发展。绥靖者常常同意将第三国的全部或部分领土让与其强大敌人。
跟着强者走的国家不会竭尽全力去遏制侵略者,但绥靖者不同,它仍要遏制威胁。然而,如同跟着强者走一样,绥靖也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思想相抵触,因而,它是一个离奇而危险的战略。
出于现实主义原因让与权力
不过,在有些特殊情况下,大国可能会向另一国让与权力,而这种行为并不违背均势逻辑。如前所述,有时推卸责任者允许责任承担者获得权力是很有意义的,如果这种做法能增加责任承担者单独遏制侵略者的前途。另外,倘若一个大国同时面对两个或更多侵略者,而它既无资源遏制所有这些对手,又没有盟国供它推卸责任,那么被困扰的国家可能会区别威胁的优先次序,允许自己与威胁较小一方的均势局面出现逆转,以便腾出手来对付首要威胁,如果运气好的话,次要威胁最终会成为主要威胁的敌人,从而实现与前者结盟反对后者的目标。
最后,处于短期战略考虑,以便争取时间动员遏制侵略的必要资源而向一个危险的对手让与权力,也是有意义的。实施让与的国家不但要应付短期的脆弱形势,而且要具有高超的长期动员能力。
结论
最后一个任务是关于国家如何获取和维持令人关注的权力的。
大国不但仿效彼此的成功实践,同时也重视创新。国家通过发展新式武器、创新军事思想或聪明战略,寻找新办法以获取比对手更多的优势。重要的利益常常出现在表现不俗的国家身上,这就是国家对出其不意的战略感到极度担心的原因。……换句话说,安全竞争促使国家背离了被接受的实践和对实践的遵循。
注释:本书中所使用的“侵略者”指既有动机又有资本运用武力获得额外权力的大国。正如第二章所强调的,所有的大国都有侵略的意图,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具有采取侵略行为的能力。
第六章 行动中的大国
日本(西元1868-1945年)
目标和对手
日本的扩张记录
德国(西元1862-1945年)
目标和对手
德国的扩张记录
苏联(西元1917-1991年)
目标和对手
苏联的扩张记录
意大利(西元1861-1943年)
目标和对手
自由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的扩张记录
自我拆台的行为?
核武器竞争
美国的核政策
苏联的核政策
对于核革命的误解
结论
在大多数情况下,本章讨论的例子中,大国都采用积极的手段来获得相对于其对手的优势——正如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们预测的那样。
第七章 离岸平衡手
美国的崛起(西元1800-1900年)
天定命运论
必要的战略措施
美国与欧洲(西元1900-1990年)
美国与东北亚(西元1900-1990年)
英国大战略(西元1792-1990年)
结论
第八章 均势与推卸责任
作者已在第五章中说过,均势和推卸责任是国家用以保卫均势,反对入侵者的主要策略。被威胁的国家怀有强烈的动机去推卸责任。之所以倾向于推卸责任而不是均势,是因为一旦威慑失败,成功的责任推卸者不必非要与入侵者交战。事实上,如果入侵者和承担责任者陷入一场长期代价高昂的战争,推卸责任者甚至还可获得权力。尽管这种推卸责任具有进攻性特点,但总有这种可能,即入侵者会赢得迅速而决定性的胜利,使均势朝着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推卸责任者的方向变化。
本章由三个目的。首先,作者解释被威胁的国家何时倾向于追求均势,何时倾向于推卸责任。这种选择主要是国际体系结构作用的结果。在两极体系中,受威胁的大国必须去抗衡其对手,因为没有其他大国来承担责任(catch the buck)。在多极体系中,被威胁国家能够而且经常推卸责任。发生推卸责任的次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威胁的程度与地缘因素。当没有要对付的潜在霸主,以及当被威胁国家不与入侵过接壤时,多极体系中推卸责任很普遍。但是,就算有一种支配性威胁,被威胁国家仍然会寻求机会去推卸责任。一般而言,潜在霸主控制越多的相对权力,体系中所有被威胁国家就越有可能摒弃推卸责任而形成一种均势联盟。
第二,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欧洲五个安全竞争最激烈的例子,来验证作者的关于被威胁国家何时推卸责任的观点。
第三,作者希望明确其观点,在面临入侵者时被威胁的国家倾向于推卸责任而非抗衡之。
国家何时推卸责任?
推卸责任行为在不平衡的多极体系中经常发生。
总之,在两极体系下大国推卸责任是不可能的,而在多极体系中不仅可能而且很普遍。事实上,仅当存在一个非常强大的霸主以及入侵者与被威胁大国不存在缓冲地带时,多极体系中可能没有推卸责任行为。在缺乏支配性威胁与共同边界时,相应地在多级体系中就可能有实质性的推卸责任行为。
大革命时期及拿破仑时期的法国(西元1789-1815年)
背景
大国的战略行为
权力的计算
俾斯麦的普鲁士(西元1862-1870年)
背景
大国的战略行为
权力的计算
威廉德国(西元1890-1914年)
背景
大国的战略行为
权力的计算
纳粹德国(西元1933-1941年)
背景
大国的战略行为
权力的计算
冷战(西元1945-1990年)
背景
大国的战略行为
权力的计算
结论
进攻性现实主义预测国家对均势十分敏感,会寻找机会来增加自身实力,或削弱对方实力。在现实条件下,这意味着国家将采纳反映了由权力特别分配所产生的机遇与限制的外交策略。
总之,地缘因素与权力分配在被威胁大国面对危险的入侵者时,是决定形成均势联盟还是推卸责任这一问题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下章将转而讨论入侵者,关注它们何时可能对另一国家发动战争,很明显权力分配对解释大国战争爆发也很重要。
第九章 大国战争的原因
进攻性现实主义既考虑极的数量又考虑体系中主要国家间的均势,同意两极比多极更稳定的观点,但进一步将多极体系分为是否存在潜在的霸主。
结构与战争
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最关键的是大国数目及各方控制有多少权力。体系可能是两极的也可能是多极的,它在主要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平均程度也参差不齐。所有大国间的权力比(power ratio)影响了国际体系未来的稳定性,但体系中两个最了不起的国家间的权力比是关键。
两极和多极
战争在多极体系中比在两极体系中更可能爆发,原因有三。首先,有更多的战争机会,因为在多极体系中存在更多的潜在冲突双方。第二,在多极世界中权力不平衡的现象更普遍,这样大国更可能拥有赢得战争的能力,这就是威慑更困难而战争更有可能爆发。第三,误算的潜在性比在两极体系中更大:国家或许认为它们有能力去压制或征服另一个国家,而事实上它可能没有这种能力。
【注:第三,书上写的是”比多极体系“,感觉这里翻译错了,故改正下。看后文,确实是翻译错了。】
战争的可能性
非均势
误算的可能性
平衡的多极与不平衡的多极
总结
近代欧洲的大国战争(西元1972-1990年)
分析
结论
任何时候当多极体系包含拥有最强大军队和最富有的国家时,大国间战争就更可能爆发。
第十章 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对中国崛起有些重要见解。一言以蔽之,作者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如果继续增长,就会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美国却要全力以赴阻止中国取得地区霸权。而中国的大部分领国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和越南会联合美国遏制中国权力。结果将是激烈的安全竞争,战争颇有可能。说简单点,中国崛起之路大概并不平坦。
【注:杜鲁门和马歇尔早就这么干了!现在的情况无非是马克思主义者争教门。】
本章余下的内容将这样安排。下节简要回顾作者的理论的核心内容,该理论详见第二章。之后总结作者对美国西半球霸权之路的讨论,该问题在第七章种已讨论得颇为详细。从中可以清楚看出美国开国以来大部分的时候都按进攻性现实主义行事。再下一节的重点是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会怎么行事。作者坚持认为中国也会遵循他的理论,也就是说实际上会效仿美国。接下来一节作者将解释美国和中国的邻国为什么可能组成制衡联盟来遏制中国。之后作者将考虑中美开战的可能性有多大,认为中美之间比冷战期间的超级大国更可能开战。倒数第二节还要试反驳两种反对作者所作悲观预测的意见。最后一节简短总结本章,指出作者若是预测错误,最可能的原因是社会科学理论总有局限性。
进攻性现实主义概述
归根结底,作者的理论就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迫使关心自身安全的各国争夺权力。大国的最终目的都是尽可能攫取世界权力,最终支配国际体系。具体来说,就是最强大的国家总想称霸所在地区,并确保没有竞争性大国支配其他地区。
本理论首先对世界作出五点假设,都是合理地接近于现实。首先,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关键行为体,其上再无权威。
有两点假设是关于国家能力(capabilities)和国家意图(intentions)的。
本理论还假设国家把生存(survival)列为最高目标。……最后一点假设是,国家是理性行为体(rational actor),也就是说各国都能制定使本国生存概率最大化的战略。
所以总体来说,要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生存下来,最好的办法是当独一无二的地区霸主。
美国的霸权之路
踏着山姆大叔的足迹
中国式的权力政治
但更有可能的情况却是,中国会寻求发展经济,挟强大的国力为邻国划定可接受行为的界限,并明示要是邻国不守这种规矩,就要付出沉重代价。说到底,这就是美国在西半球做过的事情。
不仅如此,还有不少证据表明中国领导人希望获得能把美国海军赶出第一岛链(first island chain)的能力,第一岛链一般来说包括大巽他群岛、日本列岛、菲律宾诸岛屿和台湾岛。中国若成功,就能封闭东海、南海和黄海,战端一起,美国海军便几乎不可能达到韩国。而且中国国内还有言论,要最终把美国海军赶出第二岛链(second island chain),这一链从日本东海岸到关岛(Guam),然后下接摩鹿加群岛(Moluccan Islands)。其中还包括不少小岛群,如小笠原群岛(Bonin Islands),加罗林群岛(Caroline Islands)和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s Islands)。中国一旦成功,日本和菲律宾就将得不到美国海军的支援。
中国追求支配亚洲主要是为了尽可能确保安全,但还有一个原因,与中国和部分邻国的领土争端有关。
以上的领土纠纷对中国既然十分重要,再加上靠外交似乎难以化解,中国若要争取有利解决,最好的办法就是靠胁迫。说详细些,就是中国若是比邻国都强得多,再用军事威胁强迫对方基本按中国的意愿达成协议时就处于有利位置。如果无效,那中国总能亮剑动武来贯彻自己的意志。简言之,中国做地区霸主最有利于解决其诸多领土争端。
【注:在当前位面,不存在这样的中国。】
中国会明显想要限制美国在别处投射力量的能力,好让自己更有可能取得亚洲的地区霸权。但中国还另有理由要把美国尽可能堵在西半球。具体来说,中国在非洲具有重大的经济政治利益,而且将来似乎更大。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十分依赖海湾地区的油气,日后大概更远甚于此。中国和美国一样,都极可能把海湾地区当作自己的重大战略利益所在,所以两国最终一定会在该地区展开激烈的安全竞争,大体和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的做法一样。在西半球给美国造成问题,就能限制美国向海湾和非洲投射力量的能力。
中国崛起藏不住
有人可能说:中国确实要试图统治亚洲,但是可以以一种特定的巧妙战略,和平达到目的。这要求中国按邓小平的名言保持低调,尽可能避免卷入国际冲突。邓小平的原话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中国所以应该韬光养晦,是因为只要避开麻烦一直发展经济,最后就会强大到足以在亚洲其支配作用。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也就成为既定事实(fait accompli)。即使不能如此,最终必须以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来取得霸权并解决其面临的争端,那是中国也仍然很有条件支配邻国和美国。
【注:理论上中国确实应该韬光养晦,不过大清就得继续加速,最好向八十国宣战!保中国不保大清!】
现在就发动战争,甚至只加入激烈的安全竞争,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很不明智的。冲突会损害中国经济,中国军队也打不过美国及其现有盟国。所以中国最好还是等到力量增强,条件改善之时再对付美军。说简单些,时间在中国一边,所以中国对外政策应该低调,以免引起邻国疑虑。
实战中,这意味着中国应该全力向外部世界发出信号,表示自己意图温和, 也不打算建立强大且有威胁性的军事力量。言论上,中国各领导人应当不断强调自己的和平意图,并表示中国有深厚的儒家文化,所以能和平崛起。同时他们还应该努力防止中国官员用激烈的语言描述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也不许对其作威胁性声明。
行动上,中国不应该主动对邻国或美国挑起任何危机,别国对中国挑起危机时也不能火上浇油。比如中国应当竭尽所能,避免南海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问题给自己造成麻烦。国防开支要尽可能限制,以免看起来有威胁,同时要加强与邻国和美国的经济交往。根据这种逻辑,中国领导人应当强调中国日渐富裕而且加强经济互相依存很有好处,因为这些变化将成为推动和平的强大力量。不管怎么说,人们普遍认为在紧密联系而且繁荣的世界里发动战争无异于杀鸡取卵。最后,中国还应当在尽可能多的国际组织中扮演积极和合作性的角色,并与美国合作确保朝鲜问题得到控制。
这种办法看起来确实很吸引人,但行不通。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一国用来增进自身安全的手段往往最终有损其他国家的安全。
总而言之,中国改善其军事能力的几乎所有举措在中国自己看起来都是防御性的,但日本、越南和美国却会认为是进攻性的。所以中国的各邻国都很可能将中国改善其军事态势的任何措施不仅当作中国一心追求强大进攻能力的证据,而且也当作中国有进攻意图的证据。其中也包括中国只是对邻国或美国加强战斗力的措施作出回应的情况。
归根结底,美国和中国的绝大部分邻国都有强烈动机遏制中国崛起,所以都会密切监视中国发展,并及早出手阻止。下文就进一步讨论美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可能会如何应对中国崛起。
迅速联合,制衡中国
山姆大叔对阵中国龙
美国对付崛起中国的最佳战略是遏制(containment)。这就需要美国集中精力不让中国用军事开疆拓土,或是说得宽泛些,扩大其在亚洲的影响。为此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力争建立制衡联盟,尽可能吸收中国的邻国。最终目标是仿效北约这一冷战期间遏制苏联的极有效工具,建立起联盟结构。美国还要采取措施继续控制世界各大洋,好让中国难以把力量可靠地投射到海湾等遥远地区,尤其是西半球。
遏制本质上是防御战略,因为它不要求对中国发动战争。
美国既然是离岸平衡老手,其理想战略便是尽量只置身幕后,而让中国的邻国背起遏制中国的大部分负担。说到底就是美国会把责任转嫁给害怕中国的亚洲国家。但这办不到,原因有二。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邻国本身力量不够,控制不了中国。美国也就难有选择,只好自认先锋,将其巨大力量的一大部分集中在这个目标上。而亚洲将要加入制衡联盟对付中国的国家许多相距又很遥远,印度、日本、越南就是例子。所以要建立有效的联盟系统,就需要美国居中协调。当然冷战时美国也遇到了类似情况,它别无选择,只好一肩挑起在欧洲和东北亚两处对抗苏联的负担。总之,要是当地国家无法凭借自身实力遏制潜在霸主,离岸平衡手就必须上岸了。
还有三种战略可以替代遏制。头两种的目标分别是靠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和执行旨在减慢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策阻止中国崛起。但这两种战略美国都无法采用。第三种替代战略叫挖墙脚(rollback),虽然可以一用,效果(payoff)却只聊胜于无。
不能实行预防性战争就是因为中国有核威慑力量。……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也不支持打预防性战争。
使中国经济减速这一选项当然比核战争更有吸引力,但也一样行不通。
第三种替代遏制的战略叫做挖墙脚,实行这种战略,美国要寻求通过颠覆亲共政权,甚至也许通过在中国内部制造问题来削弱中国。
但迄今为止,遏制还是美国最有效的战略。
退一步讲,,就算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不到这种水平(前文中指韩国的水平),其潜力赶不上美国,也还是很有条件谋求亚洲霸权的。这就说明让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将来大大减缓十分符合美国利益。这种结果不一定有利于美国繁荣,更不利于全球繁荣,但会利于美国安全,这可是最重要的。
【注:美国开打贸易战、控制芯片等出口是能大大打击中国经济,大大降低了各种寄生虫的收入水平,深化内部矛盾,让“沉船计划”早日成为现实。如果能把拿美加绿卡的nmslnese送进集中营就更好了!】
中国的邻国怎么办?
基本上每个国家都得站队,不仅是因为中国和美国都要大力逼迫它们站队,而且因为这些国家大多既远弱于中国,又远弱于美国,也自然会希望在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能有个强大的保护者。
既然生存最重要,中国的大部分邻国就都会选择制衡中国,就好像冷战时东北亚和欧洲大部分能自由选择的国家都跟着美国反对苏联。原因很简单, 中国与美国相比对亚洲大多数国家威胁更大,国家一定是制衡自己最危险的敌人,而不会投靠之。中国更有威胁主要是由于地理原因。具体来说,中国是亚洲国家,与邻国不是直接接壤,就是距离近到轻易发动打击。
简言之,这种情况下经济考虑和政治军事考虑相互冲突,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最终哪个因素会占上风?作者的意见是安全考虑几乎总压倒经济考虑,国家在必须选择制衡和投靠两种战略之一时,会选择制衡而不是投靠。作者这种意见的内在逻辑应当已很清楚。国家制衡强大的对手是因为制衡最能保障生存,而生存一定是国家的最高目标。投靠更强大的国家相反会减少投靠国的生存机会,因为这样一来强国就可以不受阻碍地变得更强,也就更危险。
所谓经济强制地说法却另有一套逻辑,它强调繁荣重于生存。其核心观点是市场力量强大的国家可以沉重打击目标国经济,经济惩罚的威胁足以强迫经济脆弱的国家投靠更强的国家。严重的经济损失无疑可怕,但不能生存危险更大。换言之,生存的强制力量比繁荣更强,这就是为什么现实主义逻辑往往胜过基于经济强制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邻国会制衡中国。
安全竞争什么样?
中美若展开安全竞争,将有12种形式。首先是危机,也就是双方争议很大,很可能爆发战争。……另一种主要对抗形式是军备竞赛。……
还可能有代理人战争(proxy wars),也就是中美两国的盟国开战,中国或美国背后支持。两国也可能会寻找机会在世界各地推翻与对方友好的政权,主要靠秘密活动,有时也要公开行事。还应该会有证据表明双方都在有机会引诱对方陷入花费巨大的愚蠢战争时采取诱捕(bait-and-bleed)战略。如果还没诱,对方就自动陷入了持久战,那就可以坐观血腥厮杀(bloodletting),力争把冲突拖得越长越好。
出了战场,还会有很多证据表面两国政府官员把对方认作头号威胁。
中美两国还可能限制双方民众交往,就像苏美两国冷战期间的做法一样。而且我们也预计会看到美国不许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与武器开发有直接关系的专业,以及其他可能影响两国力量平衡的技术。两国一定会竞相对有重要国家意义的商品和服务采取选择性出口控制。对于美国来说,可能的范例是巴黎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Control,简写为CoCom),美国冷战期间成立这个组织就是要限制敏感技术传入苏联。
打不打?
亚洲地理环境
上文强调亚洲比冷战时的欧洲更可能打仗,部分是因为核升级的风险减小了。但是,未来亚洲战争中总有可能意外使用核武器,这种可能性将在危机中维护稳定。
极化与战争
亚洲多极体系更容易打仗。
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
每个民族的成员都有强烈的群体忠诚感,实际上,对民族的忠诚往往压倒了所有其他形式的身份认同。民族的大部分成员一般认为他们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团体,其历史英雄辈出,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但人们不仅只为本民族骄傲,还把它和其他民族比较,特别是那些人们常常接触、相当了解的民族。
【注:米尔斯海默这块内容写得真差,共产主义本身就是要消灭民族、国家、家庭之类的共同体,怎么可能支持民族主义呢?况且后清宪法明确反对大汉族主义,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四等汉,这怎么可能是个民族主义国家?连70多年前的杜鲁门、毛泽东都能认识到蒋介石身上的大汉族主义气息,米尔斯海默还搞不懂,当然恐怕他也搞不懂中华民族主义和汉民族主义的区别,大部分人都分不清的,世人总是存在各种误解的!事实上,大汉族主义是后清最大的威胁!后清搞计汉生育也和当年蒙元即将灭亡时伯颜“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漢人”前后相呼应。】
有时,一个民族不仅觉得自己比其他民族优越,而且最后还厌恶其他民族。作者称之为极端民族主义(hypernationalism),也就是相信其他民族不仅低劣,而且危险,所以必须严厉对待,甚至残酷对待。在这种情况下,对“他者”的轻蔑和仇恨席卷整个民族,造成用暴力消除威胁的强大动机。极端民族主义换言之也就可以成为战争的强大动力。
极端民族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安全竞争激烈,这种竞争倾向于导致有关各民族国家的人民相互妖魔化(demonize)。有时领导人将极端民族主义作为威胁夸大战略的一部分,这个战略是要让公众警惕他们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不会完全认识到的危险。在另一些情况下,极端民族主义自下而上泛起,主要是因为安全竞争中固有的卑鄙行为经常导致民族国家的普通公民鄙视敌对民族国家的几乎一切。大的危机就能火上浇油。
【注:有些情况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体现,而是基督徒对付异端和异教徒的表现!】
能不能和平崛起
儒家思想是否和平
阎学通明确指出,儒家思想强调道德,并不代表排除用战争作为治国手段。事实上儒家思想还规定中国应该在别国做出中国领导人认为是不道德的战争的行为时发动正义战争。他写道:”有人说孔孟提倡‘非战’,反对一切战争。其实孔孟并不反对一切战争,而只反对非正义战争,他们支持正义战争。”他有进一步说:“孔子认为靠教人遵守仁义的规范还不能毕竟全功,所以他认为国君无道,可以以战争方式惩治。”
【注:后清作为外来弥赛亚宗教徒,本身是极为仇视同一生态位的儒学的。无非是原有意识形态破产,把儒学拉过去遮羞罢了!墨家才强调非攻反对战争,但是得经过战争才能达到非攻境界。这和踏过血海才能到达理想的彼岸也是一类原理。】
多赚钱,少打仗
大量证据表明,相互交战的国家也经常并不断绝经济关系。
结论
阎学通对话米尔斯海默:中国能否和平崛起?
经济利益不能阻止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