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选择——个人声明
- 简介
- 概述
- 推荐序 作为目的和手段的自由
- 出版序言
- 引言
- 第1章 市场的力量
- 第2章 管理的专横
- 第3章 危机的解析
- 第4章 从摇篮到坟墓
- 第5章 生而平等
- 第6章 我们的学校出了什么问题?
- 第7章 谁在保护消费者
- 第8章 谁在保护工人
- 第9章 通货膨胀的对策
- 第10章 潮流在转变
- 附录
- 老版本出版说明
- 新版本译后记
简介
英文名: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作者:Milton Friedman & Ross Friedman
所选中文翻译版本:商务印书馆西元1982-05出版版本、机械工业出版社西元2019年10月重印版
概述
自由市场经济才能实现繁荣和自由。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政府应让市场经济自由运作不要干预,政府唯一的经济任务是维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
启示如下:
实行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单一低税制、积极不干预、无为而治、藏富于民、民富国富
限制政府权力才能保障民众的自由。
推荐序 作为目的和手段的自由
自由选择和自由贸易能比政府更有效地提升公众的福利。
出版序言
谁要是在一个晚上(或甚至十个晚上,每晚一小时)就被人所说服,那他肯定不是真的被说服、他会因为同另外一个持相反意见的人呆一晚上而改变看法。唯一真正能说服你的人是你自己。没事儿的时候,你脑袋里必须翻来覆去地捉摸这些问题,必须细细咀嚼许多论点,这样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你的临时选择才会变成坚定的信念。
引言
自从欧洲人首次向美洲殖民——1607年在詹姆斯敦,1620年在普利茅斯——以来,美国就成了一块磁石,吸引着人们,有来冒险的,有从暴政下逃出来的,或者干脆就是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谋求较好的生活的。
开始时是涓涓细流,但在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后,细流慢慢变粗,到十九世纪就成了一股洪流。千百万人不堪忍受苦难和暴政,被自由和富裕的生活所吸引,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来到了美国。
他们踏上美国国土时,并没有发现黄金铺的路;生活也不象从前想象的那么好过,但他们确实获得了自由,获得了充分发挥他们才能的机会。靠着苦干、精明、节俭和老天爷的保佑,大多数人实现了自己的希望和梦想,诱使他们的亲戚朋友也来参加他们的奋斗行列。
美国的历史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同时发生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发生奇迹,是因为美国人把两套思想付诸了实践——说来也巧,这两套思想都是在1776年公诸于世的。
一套思想体现在《国富论》里,这部伟大的杰作使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成了现代经济学之父。该书分析了市场制度为什么能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经济领域里生产我们的衣、食、住所必需的广泛合作结合起来。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见解是:参加一项交易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而且,只要合作是严格自愿的,交易双方得不到好处,就不会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和对自由的侵犯来促使人们合作。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只盘算他自己的得益”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去达到一个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目的。对于社会来说,同他的盘算不相干并不总是坏事。他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促进社会的利益,常常比他实在想促进时还更有效果。我没听说过,那些装作是为公众的利益做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第二套思想体现在独立宣言中,该宣言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表达了他的同胞的普遍情绪。它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这是历史上按照人人有权追求自己的价值的原则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创而平等,耶和华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用更为偏激和绝对的话说:
人类有理由为之个别地或集体地干涉任何一部分人的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是自我保护。……对文明社会的某一成员正当地强制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防止他对别人进行伤害。人类自己的长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不是足够的理由。……任何人的行为对社会负责的部分只是关系到别人的部分。就其仅仅关系他自己的那部分来说,他的独立按道义说是绝对的。对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身心,个人就是主宰。
美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实现独立宣言中的各项原则而奋斗的历史——开头是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最后通过一场流血的内战而解决),后来是促进机会均等的斗争,最近则是力图达到收入均等的斗争。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如果人们在没有高压统治和中央指挥的情况下能够相 互合作,那么这可以缩小运用政治权力的范围。此外,自由市场通过分散权力,可以防止政治权力的任何集中。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手里,肯定会给人民带来暴政。
十九世纪,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黄金时代。美国甚至比英国更繁荣。它以清白的历史开始:阶级和等级的余毒较少;政府的限制较少;而土地则较为肥沃,人们可以去努力开发,去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还有一片尚未开发的大陆,等待着人们去征服。
自由的繁殖力在农业上表现得最为显著。在通过独立宣言的时候,只有不到三百万欧洲人和非洲血统的黑人(即不包括印第安土著)占据着沿东海岸的一块狭长地带。当时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活动。要用95%的劳力来养活全国的人口和提供粮食剩余,以换取外国货物。今天,只用不到5%的劳力就能养活二亿二千万居民并提供大量的粮食剩余,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
这一奇迹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显然不是政府的中央指导,因为俄国及其卫星国、大陆中国、南斯拉夫和印度等国目前虽然依靠中央指导把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劳力用于农业,但仍然时常要依赖美国的农业来避免大规模的饥荒。在美国农业获得迅速发展的大部分时期,政府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可以得到土地——但却是些以前什么也不出产的地。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建立了一些由政府赠与土地的农学院,它们依靠政府的资助传播情报和技术。但是毫无疑问,美国农业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在自由市场上发挥作用的个人积极性。这个自由市场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当然,可耻的奴隶制下的奴隶是无法进入自由市场的。而最迅速的增长是在废除了奴隶制以后。千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自由地为自己而劳动,其中有些是独立的农民或工商业者,有些则按照相互协议的条件为别人工作。他们可以自由地试验新技术——试验失败的风险由自己承担,试验成功的好处归自己所有。他们得到政府的帮助极少。更重要的是,他们遭到政府的干涉极少。
政府开始在农业中起主要作用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及其以后的时期。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限制产量,以保持人为的高价。
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是靠了在自由的刺激下同时发生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了使农业发生革命的新机器。反过来,工业革命又依赖农业革命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工业和农业手携手地共同向前迈进。
斯密和杰斐逊都把政府权力的集中看作是对老百姓的巨大威胁;他们认为,不论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护公民免受政府的专制统治。这就是弗吉尼亚权利宣言(1776年)、美国权利法案(1791年)以及美国宪法中规定的三权分立的目的;也是英国十三世纪颁布大宪章和十九世纪末改革法律机构的推动力。在斯密和杰斐逊看来,政府应该是仲裁者,而不应是当事人。杰斐逊的理想,正象他在1801年的首次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那样,是建立“(一个)开明而节俭的政府,它将制止人们互相伤害,但仅此而已,在其他一切方面将放手让人们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从事自己的事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成功,减少了它对后来的思想家们的吸引力。十九世纪后期的政府受到严格限制,集权甚少,不危及老百姓。但另一方面,它的权力也很少,使好人做不了好事。在一个并非尽善尽美的世界上,还有许多罪恶。的确,正是社会的进步使残余的罪恶显得更加可恶可憎。象往常一样,人们认为事情必然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们忘记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对自由的威胁,心里想的只是更为强大的政府所能做的好事,认为只要权力掌握在“好人”手里,政府就会做好事。
这些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影响英国政府的政策。而且被越来越多的美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但直到三十年代初期的大萧条时,才开始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有所影响。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指出的,大萧条是政府在金融领域中的失败造成的。在金融领域,政府自建国初期以来就一直在行使权力。但是,政府对于大萧条的责任,当时和现在都没被认识。相反,人们却普遍认为大萧条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造成的。这个神话使公众也加入了知识分子的行列,改变了过去对于个人和政府的看法。原来人们强调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现在却强调个人应象象棋中的小卒那样由外界力量来摆布。原来认为政府的作用是充当仲裁者,防止人们互相强迫,现在却认为政府应充当家长,有责任迫使一些人帮助另一些人。
这种看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支配了美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各级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地方政府的权力和本来由地方政府掌管的事业,被越来越多地移交给了中央政府。政府以安全和平等为名,越来越经常地把从某些人那里得到的东西给与另一些人。政府制定出了一项又一项的政策来“管理”我们“对目标和事业的追求”,把杰斐逊的名言完全颠倒了过来(见第七章)。
人们本来是出于好意,是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但现在即便是最起劲地鼓吹福利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在政府活动的领域,正如在市场中一样,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它的作用正好同斯密的那只手相反:一个人如果一心想通过增加政府的干预来为公众利益服务,那他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增进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私人利益。这一结论将在本书一些章节考察政府行使权力的那些领域时得到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无论是建立安全(第四章)或平等(第五章),或是促进教育(第六章),保护消费者(第七章)或工人(第八章),还是防止通货膨胀和促进就业(第九章),总之,在政府行使权力的一切领域,都证明了这一点。
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迄今为止,“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上的大错误,使事情趋于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亚当·斯密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强大得足以克服活动在政治领域里的那只手造成的麻痹作用。
近来的经历——经济增长缓慢,生产率下降——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我们继续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政府,继续把权力授给公务人员这样一个“新的阶级”,让他们代表我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收入,那么,个人的独创性是否还能克服政府控制的麻痹作用。一个日益强大的政府迟早将摧毁自由市场给我们带来的繁荣,摧毁独立宣言庄严宣布的人类自由。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我们许多人预料的要早。
我们还没有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仍有自由选择的机会,是继续沿着“通向奴役的道路”(这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为他的一本意义深刻而颇有影响的书起的名字)疾驰下去,还是加紧对政府的限制,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人们自觉自愿的合作来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是听任黄金时代结束,而沦入大多数民族过去一直遭受而且目前仍在遭受的专制统治和苦难呢?还是运用我们的智慧、先见之明和勇气来改弦更张,记取经验教训,而从“自由的复兴”中得到好处?
如果我们要作出明智的抉择,我们就必须了解我国制度的运行所依赖的基本原则,既要了解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原则(见第一章),又要了解杰斐逊提出的政治原则(见第五章)。斯密的经济原则告诉我们一个复杂的、有组织的、顺利运行的制度为什么能在没有中央指导的情况下获得发展并繁荣兴旺,同时告诉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不采用强制性手段而使人们相互协作。我们必须懂得为什么试图以中央指导代替合作会造成那么多损害(第二章)。我们也必须懂得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密切关系。
幸好,潮流在转变。在美国、英国、西欧各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里,人们对政府作用的增大带来的威胁越来越有所认识,对所遵循的政策越来越不满。这一转变不仅反映在舆论上,也反映在政治领域里。对于我们的议员们来说,唱不同的调子乃至采取不同的行动,正在变成政治上有利的事。我们正经历着公众舆论的另一次重大改变。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使人们更加相信个人的积极性和自愿的合作,而不是转向完全集体主义的另一极端。在本书最后一章里,我们探讨为什么在一个按说是民主的政治体制里,特殊利益会压倒一般利益,探讨我们能做些什么来纠正造成这种结果的制度上的缺点,探讨怎样才能既限制政府又使它能够履行自己的主要职能。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防御外来敌人的侵略,确保我们的每一个同胞不受其他人的强迫,调解我们内部的纠纷,以及使我们能一致同意我们应遵循的准则。
本节内容概述
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见解是:参加一项交易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而且,只要合作是严格自愿的 ,交易双方得不到好处,就不会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和对自由的侵犯来促使人们合作。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只盘算他自己的得益”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去达到一个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目的。对于社会来说,同他的盘算不相干并不总是坏事。他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促进社会的利益,常常比他实在想促进时还更有效果。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如果人们在没有高压统治和中央指挥的情况下能够相互合作,那么这可以缩小运用政治权力的范围。此外,自由市场通过分散权力,可以防止政治权力的任何集中。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手里,肯定会给人民带来暴政。
在斯密和杰斐逊看来,政府应该是仲裁者,而不应是当事人。杰斐逊的理想,正象他在 1801 年的首次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那样,是建立“(一个)开明而节俭的政府,它将制止人们互相伤害,但仅此而已,在其他一切方面将放手让人们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从事自己的事业。”
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迄今为止,“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上的大错误,使事情趋于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
一个日益强大的政府迟早将摧毁自由市场给我们带来的繁荣,摧毁独立宣言庄严宣布的人类自由。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防御外来敌人的侵略,确保我们的每一个同胞不受其他人的强迫,调解我们内部的纠纷,以及使我们能一致同意我们应遵循的准则。
附录美国《60分钟节目》调查走线的中国“润人”
结合知乎问题美国《60分钟节目》调查走线的中国“润人”,准备遣返3.6万人,但中国一个都不接收。他们的结局会如何?看充满这种行为社会主义特色。
作者:Auguard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43239628/answer/3389754461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以下是一些有意思的提要
1.去年有250W起接收或者驱离来自墨西哥偷渡客的事件,其中中国移民是增长最快的群体。
2. 在他们团队摄影的4天内,有近600人从文章中的这个漏洞中进入美国。
3. 去年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案的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有3.7W人,他们告诉栏目组他们来到美国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原因。
4. 节目组问这些人怎么知道这个漏洞的,他们说在抖音上有全流程分享。
5. 节目组被其中的中产阶级,以及走线人的秩序所惊讶到了,而且他们与边管人员很配合(而且他们带着手机,笔记本电脑,穿的也很好)。
6. 漏洞所在地归于75岁的Jerry Schuster所有,他自己也是前南斯拉夫的移民。走线人就在漏洞边上安营扎寨,砍他的树取暖,等待边管接收。他估计现在每周有3000人通过这个漏洞进入美国。
7. 边管会把走线者带到就近的圣地亚哥看守所,进行背景调查和问询,一般在72小时内,他们会被释放,然后可以填写庇护申请表了。记者问为什么他们会主动被边管找到?官员说这样既安全又有效率,但在这种边境口岸申请庇护有难度,其中就包括不怎么好用的庇护申请APP。
8. 由于两国关系的原因,在2016年美国签发给中国人的签证的数量是220W,到了2022年,这数字变成了16W,缩水了93%。
9. Tammy Lynn是有着20年经验的中国移民律师,她表示即使这些走线者申请庇护被拒了,由于中国不接受遣返,所以他们也不会被遣返,至少她没见过。一共有3.6W中国非法移民被要求离开美国,但由于中国不接收,而美国也不能强迫中国接收,所以这些非法移民会被陷入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去年有55%的中国走线者被给予了庇护,而其他国家平均只有14%。
10. 记者问老Jerry,“你问过边关,你们就不能把这个漏洞堵上吗?”。Jerry回答,是的,他们说“这事情我们管不了,你得打电话给华盛顿。”于是记者就质问了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他们回答道:他们没有权力阻止走线者通过这个漏洞进入美国,只能在他们非法进入后逮捕他们。至于堵上漏洞这个问题,他们回应到: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但需要国会给我们批钱。
最后发下油管下面的高赞评论:
- 在这个国家我们真的很愚蠢(2.8K赞)
- 太疯狂了(1.3K赞)
- 如果老Jerry租了一个超大推土机,把漏洞平了并堵上一块大石头,会发生什么?他会因阻止大量非法移民而被逮捕吗?(400赞)
- 这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260赞)
- 他们能够光明正大地进来真是太疯狂了(500赞)
报道被马一龙转发了

附录罗斯巴德批评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豆瓣用户久道短评:
我们的常识是,亚当·斯密是现代自由市场理论的奠基人,但罗氏以详实的经济史资料证明,此人不但大量抄袭,而且浪得虚名,远不及当时法国的杜尔阁等人。他否定了价值的主观性,将其视为对应了某种劳动时间的客体,这就为李嘉图以及随后马克思等提出“剥削”理论奠定了基础。斯密蔑视消费的主观性,他也无视放债的时间主观性,因此反对民间融资。他的思想,其实有浓厚的加尔文疯子色彩。通过罗氏分析,新教、加尔文最早都是与反动王党、乌托邦主义、重商主义结盟的。
附录《自由平等博爱》批判穆勒
附录【吴钩】“王安石变法”与“罗斯福新政”有什么关系?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赐稿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辛丑十一月十三日戊戌
耶稣2022年1月16日

钱穆曾讲过一件佚事:“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指常平仓制度),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忱。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
钱穆所述确有其事,华莱士访华的时间是1944年,当时媒体亦有报道:“华氏(即华莱士)研究中国历史,对于吾国王安石之农政,备至推崇,迭次言论中皆有向往之词”;在与中方接待人员谈话时,华莱士“亦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关各节,华氏誉王安石为中国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发表演讲时,华莱士又说,“彼(即王安石)于一○六八年在重大困难之下,所遭遇之问题与罗斯福总统在一九三三年所遭遇之问题,虽时代悬殊,几乎完全相同,而其所采方法,亦非常相似”。
按华莱士此说,宋代中国的王安石变法居然与20世纪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产生了联系。
众所周知,上世纪20年代末美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胡佛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应对危机失败,1932年罗斯福击败胡佛,当选美国总统,并于次年开始推行具有明显干预主义色彩的新政,其中的农业新政就是由时任农业部长的华莱士操刀的。华莱士自述:“我任农业部长后,不久就请求国会在美立法中加入中国农政的古法,即‘常平仓’的办法。这个常平仓的名字,我是得自陈焕章所著的《孔子与其学派的经济原则》。”
陈焕章,康有为弟子,光绪三十年进士,随后赴美留学,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出版论著《孔子与其学派的经济原则》(今译《孔门理财学》),1930年再版。陈焕章以现代经济学的概念与语言向西方社会介绍了传统中国的经济学说与与经济制度,其中包括常平仓制度与王安石新法,在西方反响很大,引起了经济学家凯恩斯、熊彼特、社会学家韦伯的注意。华莱士正是通过阅读陈焕章的著作,了解了传统中国的常平仓制度,以及由常平仓制度改良而来的王安石“青苗法”(又称“常平新法”)与“市易法”(又称“常平市易”)。
罗斯福新政期间,华莱士参考常平仓制度、王安石“青苗法”与“市易法”,制订了一系列农业新政,包括:1)农业部成立“商品信贷公司”,向农场主、农民提供以农产品为抵押的贷款;2)设立“联邦剩余商品救济公司”,通过收购过剩农产品再分发给城市贫民的方式稳定农产品市场价;3)联邦剩余商品救济公司还具有常平仓的功能,在丰年收购、储藏五种农产品(玉米、小麦、稻谷、棉花与烟草),以备灾荒,歉年则抛售储备的农产品;4)当“常平仓”的储备过剩时,国家对农产品销售实施配额制。
-195.jpg!article_800_auto)
从罗斯福政府的农业新政,确实可以看到王安石“青苗法”、“市易法”的影子,华莱士称王安石变法与罗斯福新政“所采方法,亦非常相似”,并非虚言。因此,一些研究者坚定地相信,“青苗法和市易法等措施是美国‘常平仓计划’的制度原型。王安石对华莱士的影响线路主要从陈焕章而起,当时有关中国古代思想的大量文献,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变法的青苗法和市易法内容直接影响到他。”
美国人华莱士对王安石变法的重新发现、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经济危机的成功挽救,也许正好印证了陈焕章的一个论断:“对我们而言,《周礼》中的某些法规(即王安石的新法)似乎可以应用于现代民主社会。以政府借贷为例,……如果在各方面都具备优良的管理制度,那么,政府最薄息的借贷不仅帮助了处于困难中的民众,而且,也增加了国家的收入。王安石确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他却生不逢时。”
第1章 市场的力量
每天,我们每一个人为了吃、穿、住,或干脆为了享乐,消耗无数的货物和劳务。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什么时候我们要买这些东西,就能买到。我们从不停下来想一下,有多少人这样那样出了力,提供这些货物和劳务。我们从不问一问自己,为什么街角那个小店——或者现在的超级市场——的货架上总有我们想买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能够挣到钱来购买这些货物。
人们自然可以假设,一定有谁在发号施令,保证以“适当的”数量生产“适当的”产品,投放到“适当的”地方。这是一种协调大批人活动的方法,即军队的方法。在军队里,将军下命令给上校,上校给少校,少校给中尉,中尉给军士,军士再下命令给士兵。
但是,完全靠这种方法或主要靠这种方法,只能指挥一个很小的集团。即使是最专断的家长,也不可能完全靠命令来控制家里其他成员的每一行动。没有哪一支庞大的军队能够真正完全靠命令来统率。将军显然不可能掌握必要的情报来指挥最低级的士兵的每一行动。在指挥系统的每一级,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必须注意考虑特殊情况,即考虑上级不可能了解的情况。指挥必须以自愿的合作来补充——这种合作不那么明显可见,比较难于捉摸,但却是协调大批人活动的最为基本的方法。
……
这种自发的市场因素虽然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抵触,但却获得了很大发展,因为要消灭它们,代价太大。自留地是可以被禁止的,但人们一想起三十年代的饥荒,便感到不寒而栗。现在苏联的经济已很难说是高效率的典范了。要不是有那些自发的因素,它运行的效率肯定还会更低。最近柬埔寨的经验悲剧性地说明,完全不要市场,会使人们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正如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完全按指挥原则运行那样,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完全通过自愿的合作来运行。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些指挥的成分。它们可采取多种形式。可以是直截了当的。如征兵,禁止买卖鸦片或甜味素,法院禁止被告或要求被告采取某些行动;也可以是非常隐蔽的,如征收重税来劝阻人们吸烟——如果这不算命令的话,可以说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一种暗示。
两者如何搀合,关系极为重大。或是自愿的交易基本上是地下活动,其发展是由于占支配地位的指挥成分过于死板;或是自愿的交易成为主要的组织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指挥成分的补充。地下的自愿交易可以防止统制经济崩溃,可以使它艰难地运行,甚至取得某些进展。对于主要以统制经济为基础的专制统治来说,它起不了什么破坏作用。另一方面,自愿交易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内部就具有促进繁荣和人类自由的潜力。它也许在这两方面不能完全发挥其潜力,但就我们所知,凡达到过繁荣和自由的社会,其主要组织形式都必然是自愿交易。不过我们要赶紧补充一句:自愿交易并不是达到繁荣和自由的充足条件。这至少是迄今为止的历史教训。许多以自愿交易为主组织起来的社会并没有达到繁荣或自由,虽然它们在这两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独裁社会大得多。但自愿交易却是繁荣和自由的必要条件。
通过自愿交易进行合作
有一个有趣儿的故事,名叫“小铅笔的家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自愿的交易怎样使千百万人能够互相合作。
价格的作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的主要思想,简单得常常使人发生误解:如果双方的交换是自愿的,那就只有在他们都相信可以从中得益时,才会做成交易。经济上的谬论,大都是由于人们忽视了这个简单的道理,而往往认为,就那么一块饼,一方要多得就必得牺牲另一方。
斯密的这一见解在两个人之间的简单交易中是容易理解的。但要懂得它怎么能使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合作来促进他们各自的利益,就困难多了。
【注:财富是创造出来的,自发交换显然有助于实现帕累托最优!】
亚当·斯密的天才的闪光在于他认识到,在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愿交易中——简单地说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出现的价格能够协调千百万人的活动。人们各自谋求自身利益,却能使每一个人都得益。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秩序可以作为许多各自谋求自身利益的人的行动的非有意识的结果而产生,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思想,直到今天仍不失其意义。
【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第二十》)
价格制度运行得这样好,这样有效,以至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感觉不到它。直到它的运行受到阻滞,我们才认识到它的良好作用,但即使到那时,我们也很少认识到麻烦的根源。
1974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石油禁运之后突然出现的排长队买汽油的现象,和1979年伊朗革命后的春夏两季再度出现的同样现象,是最近这方面的显著例子。这两次石油危机,使原油的进口供应陷入了极度混乱的状态。但这在完全依靠进口石油的日本和西德并没有导致人们排队买汽油。而在自己生产许多石油的美国却导致了排长队,其原因,也是唯一的原因,是由于政府部门执掌的法规不允许价格制度起作用。在一些地区,价格被指令控制得过低,而价格稍高一点本来是可以使加油站有足够的油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的。石油按命令分配给全国各地,而不是按在价格上反映出来的需求的压力,其结果是在一些地方过剩,而在另一些地方是缺货和排长队。价格制度的顺利运行——数十年来它保证了每个消费者能够随自己的便在任何一个加油站不必怎么等待就买到汽油——被一种官僚主义的即兴之作代替了。
价格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起三个作用:第一,传递情报;第二,提供一种刺激,促使人们采用最节省成本的生产方法,把可得到的资源用于最有价值的目的;第三,决定谁可以得到多少产品——即收入的分配。这三个作用是密切关联的。
传递情报(信息)
假设,不管是什么原因,对铅笔的需求有所增加——也许是因为出生的孩子多增加了学生人数。零售商发现铅笔的销路增加了。他们会向批发商定购更多的铅笔。批发商会向制造商定购更多的铅笔。制造商会定购更多的木料、黄铜、石墨——用于制造铅笔的所有各种产品。制造商为了使他们的供应者更多地生产这些产品,就得出更高的价钱。较高的价钱会促使供应者增加他们的劳动力,以便应付增加了的需求。为了得到更多工人,他们就得出较高的工资或较好的工作条件。这样,就象水波似的愈来愈扩大,把消息传给全世界,知道对铅笔的需求增加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对某种他们生产的东西的需求增加了,他们可能知道其原因也可能不知道其原因。
价格制度只传递重要的情报,而且只传递给需要知道的人。举例说,木材商并不需要知道,铅笔的需求增加是因为小孩出生得多还是因为有一万四千份政府公文要用铅笔填写。他们甚至无需知道铅笔的需求增加。他们只需要知道有人愿意为木料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这个价钱会维持很久,值得去满足这种需求。这两种情报都来自市场价格——前一种来自现时价格,后一种来自期货价格。
要有效地传递情报,一个大问题是保证每一个能使用这种情报的人得到它,不让那些不需要它的人把它束之高阁。价格制度自动解决了这个问题。传递情报的人受到一种刺激,去寻找能使用情报的人,而且他们最后是能够找到的。能够使用情报的人也受到一种刺激去获得情报,而他们最后也是能够得到情报的。铅笔制造商同卖给他木料的人接触。他总是试图找到新的供应者,能够提供较好的产品或是要较低的价钱。同样,木材商人同他的顾主接触,并总是试图找到新的顾主。另一方面,那些眼下不从事这些活动而且将来也不打算从事这些活动的人,则对木料的价格不感兴趣而予以漠视。
【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只能缓解,而不能消除!】
通过价格传递情报,当今由于有组织良好的市场和专业化的消息传送设施,而大为方便了。看一看《华尔街日报》上每天的行情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且不说许多更专业化的商业出版物。这些价格几乎是当即反映全世界发生的事情。在遥远的一个主要产铜国家发生了革命,或是由于其他原因,铜的生产中断,铜的现价会立刻陡涨。要了解熟悉行情的人估计铜的供应会受多久的影响,你只需要查一下同一版上的期货行情就行了。
即使是《华尔街日报》的读者,大多也只关心少数几种价格。他们可以不管其他的价格。《华尔街日报》提供这种情报,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也不是因为它认识到这个经济的运行是何等重要。促使它提供情报的,就是那个它促进其运行的价格制度。它发现,公布这些价格——即另一套价格传递给它的情报——能增加报纸发行量从而赚更多的钱。
价格不仅把情报从最终的购买者那里传给零售商、批发商、制造商和拥有各种资源的人,它们还以其他方式传递情报。假定有一处森林失火或是工人罢工,使木材供应减少而木材的价格上涨,这就告诉铅笔制造商应该少用木料。如果还生产原先那么多铅笔而又不能加价售出,那就要吃亏。铅笔的产量缩减,会使零售商提高价格,而加价会使使用者把铅笔用得更短或者改用自动铅笔。使用者用不着知道铅笔为什么涨价,而只需知道铅笔涨价就行了。
阻止价格自由地反映供求状况,会妨碍情报的精确传递。私人垄断——由一个生产者或生产者卡特尔操纵一种特定的商品——就是一个例子。这并不妨碍通过价格制度传递情报,但它的确歪曲所传达的情报。1973年石油卡特尔把油价提高三倍,传递了很重要的情报。但是这个价格所传递的情报并不反映石油供应的突然减少,也不反映关系到未来石油供应的新技术知识的突然发现,或是别的什么能够确实影响石油和其他能源供应的事情。它只是传递了这样一个情报:一些国家成功地达成了定价和分销协议。
美国政府对石油和其他能源实行价格管制,妨碍了价格把石油卡特尔的影响精确地传送给用油者。其结果是,由于不让价格的上涨来促使美国消费者节约石油而加强了石油卡特尔的地位,同时迫使美国建立庞大的控制机构,来分配不足的供应(一个能源部1979年开支约一百亿美元,雇用了两万人)。
私人对于价格的歪曲固然重要,但在当今,政府是对自由市场制度的主要干扰源。干扰的方法是征收关税和对国际贸易实行其他限制,采取冻结或影响价格(包括工资)的国内措施(见第二章),管理某些行业(见第七章),以及采取货币和财政政策来造成反常的通货膨胀(见第九章)。
反常的通货膨胀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之一,可以说是使价格传递情报的作用失灵。例如,如果木材的价格上涨,木材制造商无法知道这是因为通货膨胀使物价普遍上涨呢,还是因为在涨价前木材同其他产品相比,需求有所增加而供应有所减少。对于组织生产来说,重要的是关于比较价格即一种东西和其他东西相比的价格的情报。高度的通货膨胀,特别是变化无常的通货膨胀使这种情报陷于无意义的静态。
刺激(激励)
精确情报的有效传递,如果不能刺激有关的人去根据这种情报采取适当的行动,那传递情报就毫无意义。如果有人告诉木材生产者市场对木材的需求有所增加,但这并没有刺激木材生产者生产更多的木材来对涨价作出反应,那就没有必要告诉他这件事。自由价格制度的妙处之一是,传递情报的价格也提供刺激,使人对情报作出反应,还提供这样做的手段。
价格的这个作用同第三个作用——决定收入的分配——密切关联,不把后者考虑在内就说不清楚。生产者的收入——他的活动所得——取决于他出售产品的所得和制造产品的开销之间的差额。他反复权衡二者,最后确定的产量使他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再多生产一点会使增加的成本同增加的收入相等。而价格的提高改变了这种状态。
【注: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即边际利润=0】
一般说来,他生产得越多,生产的成本也越高。他必须采伐更偏僻或其他条件更差的地方的树木;他必须雇用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人,或者付出较高的工资以从其他行业吸引熟练工人。但是现在价格提高了,使他能够承受较高的成本,这就提供了增加生产的刺激和这样做的手段。
价格还提供另外一种刺激,使人不仅按关于需求增加的情报行动,还按关于最有效的生产方法的情报行动。假定有一种木材因短缺,而比别的木材贵,铅笔制造商便获得这种木材涨价的情报。由于他的收入也取决于售货所得和制造成本之间的差额,他就受到一种刺激去节省那种木材。换一个例子,伐木工人使用链锯还是手锯,那要看链锯和手锯的价格,哪一种成本低,要看每种锯需要的劳动量以及不同种劳动的工资。因而伐木行业受到一种刺激去获得有关的技术知识,并把它同价格所传递的情报结合起来,以最大限度降低成本。
还可以举另一个更为有趣的例子来说明价格制度的微妙作用。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石油的价格,增加了使用链锯的成本,使情况变得稍稍对手锯有利。如果这个例子似乎太牵强,不妨想一想石油涨价对运送木材的两种卡车的影响,一种是烧柴油的,另一种是烧汽油的。
把这例子推进一步,石油的涨价,就其容许发生的程度来说,增加了用油多的产品的成本,增加的幅度要大于用油少的产品的成本。因而消费者受到一种刺激而改用后一种产品。最明显的例子是人们从前喜欢体积大的汽车,现在喜欢体积小的汽车,从前用石油取暖现在改用煤炭或木柴取暖。让我们进一步来看更深远的影响:生产成本的增加或需求量的增加(由于把木头作为替代能源),使木材的比较价格上涨,由此引起的铅笔的涨价,这给消费者一种刺激,使之节约铅笔;凡此种种,价格的变化会带来无穷的影响。
迄今我们只论述了价格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刺激作用,实际上它对其他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和工人也起作用。木材需求量的增加会使伐木工人的工资提高。这是一种信号,表明对那种劳动的需求增加了。工资的提高刺激了人们,使一些原来不想当伐木工人或干其他活儿的人现在愿意当伐木工人了。进入劳动市场的年青人更多地成为伐木工人。在这里,政府和工会的干预同样会歪曲所传递的情报或阻碍个人根据情报而自由行动,前者的干预手法是规定最低工资,后者的干预手法是限制人们进入这个行业(见第八章)。
关于价格的情报——不论是各行各业的工资或地租,还是资本用于各种用途带来的收益——并不是唯一关系到决定如何使用某一种资源的情报。它甚至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情报,特别是当关系到如何使用自己的劳动的时候。最后的决定除价格外,还取决于个人的兴趣和本事——即取决于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称之为一种职业的、货币的或非货币的全部有利之处和不利之处。对一种职业感到满意可以补偿较低的工资。另一方面,较高的工资可以补偿不惬意的工作。
收入的分配
我们知道,一个通过市场获得收入的人,他的收入取决于他出售货物和劳务的所得同他在生产这些货物和劳务时所花费的成本之间的差额。所得主要是直接付给我们拥有的生产资源的款项——如付给劳动的工资或付给土地建筑物或其他资本的使用费。企业家——如铅笔制造商——的情况形式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他的收入也取决于他拥有的每一种生产资源的多寡,取决于市场为使用这些资源确定的价格。不过企业家拥有的生产资源主要是组织企业,协调企业资源以及承担风险等方面的能力。他也可以拥有一些企业所使用的生产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收入,部分就取自使用这些资源的市场价格。同样,现代公司的存在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我们泛泛地说到“公司收入”或有收入的“企业”。这是比喻的说法。实际上,公司是业主即股东和除股东资本(公司所购买的这种资本的劳务)外的资源这二者之间的媒介。只有人才得到收入,他们通过市场,从他们拥有的资源上面得到收入,不管这些资源采取什么形式,是公司股票、债券、土地还是他们个人的能力。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主要的生产资源是个人的生产能力,即经济学家的所谓“人力资本”。美国通过市场交易产生的总收入中,大约有四分之三是雇员的报酬(工资、薪金以及补助),其余部分约有一半是农场主和非农业企业主的收入,这里面既有对个人劳务的报酬又有使用企业主资本的费用。
物质资本——工厂、矿山、办公楼、商店;公路、铁路、机场、汽车、卡车、飞机、船只;水坝、炼油厂、电站;住房、冰箱、洗衣机,等等——的积累对经济增长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物质资本的积累,我们决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经济发展。不维持代代传下来的资本,一代的所得就会被下一代花光。
但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其形式是知识技能的提高、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寿命的延长——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相辅相成的。物质资本为人提供工具,使他大大提高生产力。而人能够发明新形式的物质资本,懂得使用物质资本,从中得到最大好处,并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组织使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使物质资本更富于生产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必须得到照管和替换。人力资本要比物质资本更难于照管和替换,而且照管和替换的费用更大——这就是为什么人力资本得到的报酬要比物质资本得到的报酬增长得快得多的主要原因。
我们每一个人拥有的每一种资源的数量,部分取决于偶然性,部分取决于我们自己或别人的选择。偶然性决定我们的基因,基因影响我们的体格和智力。偶然性决定我们的出身和文化环境,从而决定我们发展自己体力和脑力的机会。偶然性还决定我们可能从父母或其他施舍人那里继承的资源。偶然性可能破坏或增加我们最初的资源。但是选择也起重要的作用。我们决定怎样使用我们的资源,是勤奋工作还是随随便便,是干这一行或是另一行,是从事这种冒险还是另一种冒险,是积蓄还是花费——这些可以决定我们是消耗资源还是改善和增加资源。我们的父母、其他施舍人以及千百万可能同我们毫无关系的人的同样决定也会影响我们继承的东西。
市场为使用我们的资源规定的价格,也受偶然性和选择的影响。弗兰克·西纳特拉的嗓子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备受欢迎。要是他碰巧出生和生活在印度,是否也能受到欢迎呢?狩猎的技能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美国用处很大,而在二十世纪的美国用处就小得多了。棒球手的技术在二十年代要比篮球运动员的技术得到高得多的报酬,但在七十年代却正好相反。所有这些事情都牵涉到偶然性和选择——就这些例子来说,大多是劳务消费者的选择决定不同项目的相对市场价格。但是我们通过市场从资源的劳务上面所得到的价格也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在哪儿定居,怎样使用我们的资源,把资源的劳务出售给谁,等等。
在任何社会里,不管它是怎样组织的,总有对收入分配的不满。我们大家都感到难以理解,我们的收入为什么少于那些看来并不比我们强的人,或者,我们的收入为什么多于大多数人,他们不是也很需要,哪一方面也不比我们差吗?远处的田野总是显得更绿——于是我们就归咎于现存的制度。在统制制度下,妒嫉和不满针对统治者。在自由市场制度下,就针对市场。
结果之一是人们试图把价格制度的这种作用——分配收入——同它的其他作用——传递情报和提供刺激分开来。在美国和其他主要依赖市场的国家,近几十年的政府活动有许多就是为了改变收入分配受市场支配这种状况的,以便用另一种更为平均的方式分配收入。目前公众舆论的压力很大,要求在这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我们将在第五章里较为详尽地讨论这一问题。
如果我们不利用价格来影响收入分配,且不说完全决定收入分配,那么,不管我们的愿望如何,要利用价格来传递情报,刺激人们行动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个人的所得如果不取决于其资源提供的劳务应得到的价格,那什么会刺激他寻找有关价格的情报或根据这个情报采取行动呢?如果不管雷德·阿德尔干不干堵塞失去控制的油井这种危险工作,他的收入都一样,那他为什么要干这样危险的工作呢?他可能因一时冲动干一会儿。但是他会以此为职业吗?如果不管努力工作与否,你的收入都一样,那你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呢?如果你费了很大劲儿找到了愿意出最高的价钱购买你要出卖的东西的买主,但实际上却得不到任何好处,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如果积累资本得不到报酬,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把现在可以享受的东西推迟到将来享受呢?为什么要积蓄呢?人们的自愿节制怎么会积累现在这么多物质资本呢?如果维持资本得不到报酬,那么人们为什么不把积累或继承的资本消耗掉呢?由此可见,如果人们不让价格影响收入的分配,他们也不能利用价格干别的事情。唯一的替代办法是实行控制。由某个政府机构来决定谁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某个政府机构来决定谁该扫街,谁该管理工厂,谁该当警察,谁该当医生。
在共产党国家,价格制度的这三种作用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的。这些国家思想意识的基础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遭受着所谓剥削,而按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一马克思的名言建立的社会则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但是,由于纯粹的统制经济是无法运转的,它们不可能把收入完全同价格分开。
对于物质资源——土地、建筑物等等——共产党国家采取了极端措施,把它们变成了政府的财产。其后果是减少了维持和改善物质资本的刺激。大家都拥有某种东西而又没有一个人拥有它,维持或改善物质资本的状况同任何人都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的建筑物——象美国的公共房屋那样——才建起一两年就显得破旧,为什么国营工厂的机器经常出故障,需要修理,为什么公民不得不求助黑市来维持他们个人使用的资本的缘故。
对于人力资源,共产党政府没有能够走得象处理物质资本那么远,虽然它们曾经尝试过。它们不得不容许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自己的命运,让他们作出自己的决定,不得不让价格来影响和指导这些决定并规定收入的分配。当然,它们歪曲了价格,不让它成为自由市场价格,但它们终究没能取消市场力量。
统制经济效率的明显低下,使社会主义国家——俄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中国——的计划人员不得不认真考虑在组织生产时更多地利用市场的可能性。在一次东西方经济学家的会议上,我们有一次听到匈牙利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侃侃而谈,声称重新发现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成就,如果不是有点多余的话。他试图改造这只手,想利用价格制度来传递情报和有效地组织生产,但不让它分配收入。不用说,他在理论上失败了,正如共产党国家在实践上遭到了失败一样。
【注:最新版本中这里删改挺严重。】
更广泛的见解
人们一般认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只对货物或劳务的买卖起作用。但经济活动并不是人类活动的唯一领域,在其他领域里,也同样是在每个人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同其他人合作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了错综复杂的结构。
让我们以语言为例。语言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结构,但却秩序井然,丝毫不乱,这并非有任何中央机关在计划它。没有人决定什么词该用到语言里,文法应该是什么样,哪些词应该是形容词,哪些词应该是名词。法兰西学院倒是试图控制法国语言的变化。但为时已晚。它建立时,法语早已成了结构精巧的语言,它只不过是批准已经发生的变化而已。其他国家还很少设立这样的机构来控制语言。
语言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语言的发展同经济秩序通过市场而发展的过程很相象,也是由于个人之间自愿的相互作用造成的,不过在这里相互谋求交换的是思想、情报或传闻,而不是货物和劳务。人们赋予一个词这样或那样的意义,或者当需要的时候创造新词。人们越来越多地按某种顺序运用语言,后来就形成了规则。愿意相互交流思想的双方对他们所使用的词规定相同的意思,由此而得到了便利。当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时,一种共同的用法就传开来,这个词也就被收入了字典。在这里,没有任何强制,没有中央计划人员发号施令。不过近来公立学校在使字词的用法标准化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个例子是科学知识。各学科的结构—一物理学、化学、气象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并不是任何人深思熟虑的产物。它象托普西(译注:小说中一孤儿名,她毫不费劲地成长)那样,“只管一个劲儿地成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者们感到这样方便。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各种需要的发展而变化的。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与经济市场的发展极其相似。学者们相互合作,因为他们发现这样做相互有利。他们从相互的工作中接受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他们通过交谈、传阅未出版的材料、出版杂志或书籍等方式交换研究成果,合作是世界范围的,就象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学者同行们的尊敬和赞同所起的作用,同货币报酬在经济市场上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为了博得人们的尊敬,让同行接受他们的成果,学者们往往在最有科学价值的方面下功夫。一个学者在另一学者的成果上发展,使总体比单个加在一起的总和更大。他的成果反过来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正如现代的汽车是货物自由市场的产物一样,现代物理学是思想自由市场的产物。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科学知识的发展也受到了政府干预的许多影响,这种干预影响了资源的利用和社会需要的知识的发展。不过到目前为止,政府的影响还不是特别严重的。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曾经强烈赞成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中央计划的学者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由政府对科学进行中央计划会给科学的发展带来多么大的危险。他们担心各门学科的先后发展顺序将由上面来确定,而不是通过科学家的探求和摸索自然而然地形成。
一个社会的价值准则、它的文化、它的社会习俗,所有这些都是通过自愿的交换和自发的合作发展起来的,其复杂的结构是在接受新东西和抛弃旧东西、反复试验和摸索的过程中不断演变的。举例来说,没有哪一个君王规定过,加尔各答居民欣赏的音乐应该根本不同于维也纳居民欣赏的音乐。各国大不相同的音乐史,没有经过任何人的“规划”,而是通过一种与生物进化相平行的社会进化发展起来的。当然,个别的君主以至民选的政府可以象大富翁那样,倡导某种音乐或资助某个音乐家,从而影响音乐的自然发展。
自愿的交换产生的结构,不论是语言、科学发明、音乐风格还是经济制度,都有其自己的生命。它们能够在不同情况下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自愿的交换能够在某些方面产生一致而又在其他方面产生不同。这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过程,它的总的运行规律不难掌握,但它所产生的具体结果却很少能被人们预见到。
上述例子不仅说明了自愿交换发生作用的巨大范围,而且还说明必须给予“私利”这个概念以广泛含义。狭隘地专注于经济市场,导致了人们狭隘地解释私利,说私利就是目光短浅的自私自利,只关心直接的物质报酬。经济学受到斥责,说它只是依靠与现实完全脱节的“经济人”来得出一般性经济结论,而这个“经济人”不过是一架计算机,只对金钱的刺激作出反应。这是巨大的误解。私利不是目光短浅的自私自利。只要是参与者所关心的、所珍视的、所追求的,就都是私利。科学家设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传教士设法把非教徒变成教徒,慈善家设法救济穷人,都是在根据自己的看法,按照他们认定的价值追求自己的利益。
政府的作用
政府是怎么牵扯进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政府是自愿合作的一种形式,是人们挑选来达到某些目标的方法,因为他们相信,政府是实现某些目标的最有效的方法。
最明白的例子是,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在哪里,也就是说可以自由选择受什么样的地方政府的统治。你决定住在这个地方而不住另一个地方,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务不同。如果它从事的活动你反对或不愿为之出钱,它们不是你赞成和愿意为之出钱的活动,那你可以迁到别处去。只要有选择,就有竞争,尽管竞争往往是有限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
然而,政府并不仅仅是一种选择。它还是一个机构,广泛地被认为拥有独断的权力,可以合法地使用强力或以强力为威胁,来使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得以合法地强制另一些人。政府的这一更为基本的作用,在大多数社会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在任一特定时期里,政府的这一作用在各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别。本书的其余部分将用许多篇幅来论述最近几十年中美国政府的作用是怎样变化的和它的活动产生了什么影响。
在开始简要地论述这一问题的时候,让我们先考虑一个看起来很不相关的问题。假设有这样一个社会,其成员希望作为个人、家庭、自愿集团的成员或有组织的政府的公民,获得尽可能多的选择自由,那政府应该起什么作用呢,亚当·斯密在二百年前最为圆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任务虽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
前两项义务是简单明了的:必须保护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免遭外国人或自己同胞的强制。没有这种保护,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选择自由。手执凶器的强盗在抢劫的时候常说,“你要钱还是要命?”这也是一种选择,但谁也不会说这是自由的选择,说受害者的交换是自愿的。
当然,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反复看到的那样,一个机构尤其是政府机构“应该”实现的目标是一回事,而这个机构实际实现的目标则是另一回事。负责建立某一机构的人的意图,同管理这个机构的人的意图往往大不相同。同样重要的是,所取得的结果常常同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大不一样。
【注:这和程序一样,代码是按照写的方式执行,而不是按照想的方式执行。】
防止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强制,需要有军队和警察。但军队和警察并不总是成功的,它们有时把权力用于同自己的职能很不相干的目的。要建成并维护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确保赋予政府的强制力量只用于维护自由,而不变成对自由的威胁。我国的创建人在起草宪法时曾为此煞费苦心,但我们却往往忽视这一点。
亚当·斯密提出的第二项义务,不仅包括警察职权范围内的事,即保护人们不受肉体的强制,而且还包括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自愿的交易,只要是复杂的或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难免有含混的地方。世界上还没有那么好的印刷品,能事先写明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事件,确切说明交易各方在每一场合下的义务,因而总得有某种方法来调解纠纷。这种调解本身可以是自愿的,无须政府插手。在今天的美国,商业合同方面的纠纷,大多靠事先选好的私人调解人来解决。为适应这一需要,产生了一个庞大的私人司法体系。但是,最后的裁决,往往仍然要由政府的司法机关来作出。
政府的这个作用还包括制定一般性规则,也就是制定自由社会的公民在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时应遵守的规则,以便利自愿的交易。最明显的例子是私有财产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我拥有一所房子。如果你驾驶私人飞机在我屋顶上方十英尺的空中飞过,这算不算“侵犯”了我的私有财产?如果是在一千英尺或三千英尺的空中飞过呢?我的产权止于什么地方,你的产权始于什么地方,并没有“自然的”规定。社会主要是靠习惯法来规定产权的含义,虽然近来立法所起的作用不断增加。
亚当·斯密提出的第三项义务,是人们最争论不休的问题。他本人认为这项义务适用的范围很窄。但有些人却一直用它来为政府开展极为广泛的活动作辩护。依我们看,斯密提出的第三项义务是政府应当肩负的一项正当义务,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加强自由社会;但政府也可以以此为理由,无限扩大自己的权力。
其所以正当,是因为通过严格自愿的交易生产某些货物和劳务花费太大。让我们来看斯密在说明第三项义务时所举的一个简单例子:城市的街道和公路可以通过私人的自愿交易来建造,费用靠征税偿付。但征税的开支同建造并维修这些街道或公路的花费相比,往往过于庞大。所谓“公共工程”,是指那些不是“为了任何个人的利益而建立和维持的工程……但它们”却值得“大社会”来建立和维持。
一个更不易捉摸的例子涉及对“第三者”的影响。“第三者”是指某一交易以外的人。这个例子说的是“烟尘的污害”。你的炉子喷出烟尘,弄脏了第三者的衣领。你无意中让第三者付出了代价。如果你愿意赔偿,他也许乐意让你弄脏他的衣领——但是要找出所有受到影响的人,或者这些人要找出谁弄脏了他们的衣领,要求你各个赔偿损失或者同他们各个达成协议,是根本办不到的。
【注:外部性
你加给第三者的影响也可能并不需他们付出代价,反倒给他们带来好处。你把房屋周围绿化得很美,使所有过往行人都享受到这景色。他们可能愿意为得到这样的特权偿付点什么,但是要他们为观看你可爱的花草而缴钱,是行不通的。
用行话来说,“外界的”或“邻居的”影响会使“市场失灵”,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让受到影响的人得到补偿或付出代价,因为这样做费用太大;第三者被强加了不自愿的交易。
我们做任何事情,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会对第三者产生一些影响,不论这种影响是多么微小,或受到影响的人距离我们多么遥远。结果,乍看起来,似乎政府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正当的,都是亚当·斯密的第三项义务所允许的。但这纯粹是误解。政府的措施也会对第三者产生影响。“外界的”或“邻居的”影响不仅可以使“市场失灵”,而且也可以使“政府失灵”。如果这种影响对于市场交易是重要的话,那它对于政府采取的旨在纠正“市场失灵”的措施多半也是重要的。私人活动对第三者的影响之所以意义重大,主要是因为难以弄清给外界带来的损失或好处。在容易弄清谁受到损失、谁得到好处而且损失、好处各有多大时,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用自愿交易代替不自愿交易,或者至少是要求得到补偿。如果你的车子撞了别人的车子,责任在你一边,那政府可以迫使你赔偿对方的损失,即使这种交易是不自愿的。如果能很容易地弄清谁的衣领将被弄脏,那你就可以赔偿将要受到影响的人,或者反过来,他们可以付钱给你,好使你的烟囱少冒些烟。
如果私人方面要弄清谁给了谁损害或好处,是困难的,那么要政府做到这一点也是困难的。因此,政府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最后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把损失加到无辜的第三者头上或者让侥幸的旁观者得到好处。为了开展活动,政府必须抽税,这本身就影响纳税人的作为——这是对第三者的另一种影响。此外,政府权力的每一次扩大,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都会增加这样一种危险,即政府不是为其大多数公民服务,而是变成一些公民压迫另一些公民的手段。可以这样说,每一项政府措施都背着一个大烟囱。
自愿安排接受第三者影响的能力,比我们骤看到时所想象的大得多。举个小例子,在饭馆里面付小费是一种社会习俗,可以使你为你并不认识或不曾见过的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反过来,也使你从另一些不知其尊姓大名的人那里得到较好的服务。不过,私人行动的确对第三者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因而政府有足够的理由采取行动。我们应当从滥用斯密的第三项义务所带来的恶果中吸取教训,但教训不是政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进行干预,而是主张干预的人要肩负严格把关的责任。我们应当对提议中的政府干预详加考察,权衡得失,再行定夺。这样做,不仅因为政府干预的看不见的代价难以估计,而且还出于其他一些考虑。经验证明,政府一旦从事某项活动,就很难停止这项活动。那项活动可能并没有带来预想的结果,但却可能不断扩大,其预算不是被削减或取消,反而是不断增加。
政府的第四项义务,是保护那些被认为不能“负责的”社会成员。亚当·斯密没有明确提到这一义务。象亚当·斯密提出的第三项义务一样,这项义务也很容易被滥用。但这是不容推卸的义务。
自由只是对于负责的个人具有实在意义。我们不相信疯子或孩子的自由。我们必须设法在负责的个人和其他人之间划一界线,但这样做却会使我们最终维护自由的目标变得极为模糊不清。我们不能断然拒绝照管那些我们认为不负责的人们。
【注:打击巨婴,人人有责!】
对于小孩子们,我们把责任首先交给他们的父母。家庭,而非个人,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组成我们社会的基本单位,虽然它已明显削弱——政府干预活动增加的一个最不幸的后果。然而,把管孩子的责任交给父母大多是权宜之计而不是一条原则。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父母比别人更关心他们的孩子,可以信赖他们会保护孩子,并保证他们成长为能负起责任来的人。但我们认为父母无权对孩子为所欲为——打他们、杀他们或者把他们卖给别人当奴隶。孩子生来就是负责的人。他们有他们的基本权利,而不只是双亲的玩物。
亚当·斯密提出的三项义务,或我们提出的四项义务,确实是“很重要的”,但它们远不象斯密所想象的那样“易于为一般人所理解”。虽然我们不能机械地根据这些义务来确定政府已经进行或打算进行的每一项干预活动是否可取,但它们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原则,可以用来权衡利弊。即使作最自由的解释,它们也屏除大部分现有的政府干预,即所有那些“不是优惠就是限制的制度”。亚当·斯密曾坚决反对这些制度,而且最后摧毁了它们,但后来它们又以如下各种方式重新出现了:关税、政府对物价和工资的管制、对从事各种职业的限制、以及其他许多背离了斯密的“简单的自然自由制度”的干预。(其中许多将在以下各章里讨论。)
实践中的有限的政府
在当今世界上,似乎到处都是庞大的政府。人们也许要问,当今是否有这样的社会:它们主要依靠自愿交易,通过市场组织它们的经济活动,其政府只限于履行我们提出的四项义务。
也许最好的例子是香港。这是与大陆中国相邻的一块芝麻粒大小的地方,面积不到四百平方英里,却拥有差不多四百五十万人口。人口的密度几乎是不可置信的,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十四倍于日本,一百八十五倍于美国。然而,香港人却享有全亚洲最高的生活水平,仅次于日本也许还有新加坡。 香港没有关税或其他对国际贸易的限制(除了美国和其他一些大国施加的一些“自愿”限制外)。那里不存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指导,没有最低工资条例,没有固定价格。居民自由自在,想向谁买就向谁买,想把东西卖给谁就卖给谁,想怎么投资就怎么投资,想雇什么人就雇什么人,想给什么人干活就给什么人干活。
政府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主要是履行我们上面所说的四项义务,而且它对这四项义务进行非常狭义的解释。它实施法律,维持秩序,提供制定行为准则的手段,裁决争端,方便交通运输,以及监督货币的发行。它为从中国去的难民提供公共住房。虽然香港政府的开支随着经济的增长也有所增加,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属于世界最低之列。因而,低税保持了刺激。工商业者既可以因成功而获利,又必须为失败付出代价。
具有几分讽刺意味的是,英国的一块直辖殖民地香港,竟然成了现代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范例。管理这块殖民地的英国官员之所以能使香港兴旺发达,是因为他们采取的政策与其母国采取的福利国家政策根本不同。
虽然香港是当代的一个杰出范例,但它并不是实践中的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社会的最重要的例子。这样的例子,我们得回到十九世纪去找。一个例子是1867年明治维新后最初三十年的日本,这我们留到第二章去说。
另外两个例子是英国和美国。在为结束政府对工商业的限制展开的斗争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对这种限制的最早的打击之一。这场斗争经过七十年,最后在1846年以取消所谓“谷物法”获胜,该法律对进口小麦和其他粮食(统称谷物)征收关税并施加其他限制。这样开始了历时四分之三世纪的完全自由的贸易,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并完成了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开始的向高度有限政府的过渡。用上面引用的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这个变化使每个英国居民享有了“完全的自由,可以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经济因此而迅速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就更显出了某些贫苦地区的惨景,对此狄更斯和当时的其他小说家都有极其生动的描述。人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英国在世界各地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增加。在上面所有一切获得发展的同时,政府开支却缩减到只占国民收入的很小一部分,从十九世纪初期的接近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降到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统治六十周年大庆时的大约十分之一,这一年可以说是英国鼎盛时期的顶峰。
美国是另一个惊人的例子。十九世纪的美国是征收关税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的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曾为之进行辩护,试图——肯定没有成功——反驳亚当·斯密主张自由贸易的论点。但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那时的关税是很低的,而且政府对国内外自由贸易没有施加多少别的限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移民入境仍然几乎是完全自由的(只是对从东方来的移民施加限制)。正如自由女神铜像上的铭文所说的那样:
给我,你们那疲劳的,你们那穷苦的,你们那挤作一团、渴望自由的人们,你们那富饶的海岸抛弃的可怜垃圾。送给我这些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我在这金门旁举灯相迎。
移民成百万到来,我们成百万地接受。他们不受任何人的干涉,自由自在地生活劳动,日子越过越好。
有些人毫无根据地把十九世纪的美国描绘成剥削成性的资本家和极端个人主义横行的时代。据说,当时垄断资本家残酷地剥削穷人,他们鼓励移民,然后敲骨吸髓地榨取他们的血汗。华尔街被描绘成了欺骗小城镇居民的恶魔,说它专门吸吮中西部农民的血,幸亏他们身体强壮,尽管受尽折磨,还是活下来了。
实际远非如此。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最初来的可能受骗,但十年二十年后仍有成百万人继续到美国来受剥削,就是不可想象的事了。他们来是因为那些先来的人大都实现了自己的希望。纽约的街道不是黄金铺成的,但是苦干、节俭和冒险精神带来了在欧洲不可想象的报酬。新来的移民从东往西扩展。随着他们的扩展,出现了一座座城市,越来越多的土地得到耕种。国家越来越兴旺发达,移民分享了繁荣。
如果农民受到剥削,他们的人数怎么会增加呢,农产品的价格确实下跌了。但这是成功的标志而不是失败的标志,它反映了机器的发展、耕种面积的扩大和交通的改善,所有这一切使农业产量急速增长。最后的证明是农田的价格不断上涨——难道可以说这是农业不景气的迹象吗?
据说,铁路大王威廉·H·范德比尔特在回答记者问时曾说:“公众真该死”。这句话后来竟成了人们指责资本家残酷无情的口实,但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正是在十九世纪,美国的慈善事业获得了蓬勃发展。私人资助的学校成倍增加;对外国的传教活动急剧扩大,非赢利的私人医院、孤儿院和其他许多慈善机构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差不多每一种慈善机构或公共服务组织,从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到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从印第安人权利协会到救世军,都是在那个时期产生的。自愿的合作,在组织慈善活动方面的效率,一点也不比在组织生产谋取利润方面的效率差。
除慈善活动外,文化事业也获得了巨大发展,不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边疆小镇,都修建了美术馆、歌剧院、博物馆以及公共图书馆,而且成立了交响乐团。
政府开支的数额是衡量政府作用的尺度。除了在几次大的战争期间外,政府的开支从1800年到1929年一直没有超过国民收入的约12%。其中三分之二是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大都用于资助教育事业和修建道路。1928年,联邦政府的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约3%。
美国的成功常常被归因于资源丰富和幅员辽阔。这些自然起了作用——但如果这些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又如何解释十九世纪的英国和日本或二十世纪的香港呢?
常有人坚持说,十九世纪的美国人烟稀少,所以政府可以限制自己的活动,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但在人口集中的现代工业社会里,政府必须起大得多的、确确实实的主导作用。这些人如果在香港呆上一小时,肯定会放弃这种看法。
我们的社会是我们自己建立的。我们可以改变各种制度。物质的和人的特性限制了我们选择的余地。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这些都阻止不了我们去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它主要依靠自愿的合作来组织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它维护并扩大人类的自由,把政府活动限制在应有的范围内,使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让它变成我们的主人。
【注:事在人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本节内容概述
自愿交易并不是达到繁荣和自由的充足条件。这至少是迄今为止的历史教训。许多以自愿交易为主组织起来的社会并没有达到繁荣或自由,虽然它们在这两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独裁社会大得多。但自愿交易却是繁荣和自由的必要条件。
价格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起三个作用:第一,传递情报;第二,提供一种刺激,促使人们采用最节省成本的生产方法,把可得到的资源用于最有价值的目的;第三,决定谁可以得到多少产品——即收入的分配。这三个作用是密切关联的。
亚当·斯密: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任务虽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
政府的这个作用还包括制定一般性规则,也就是制定自由社会的公民在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时应遵守的规则,以便利自愿的交易。
政府的第四项义务,是保护那些被认为不能“负责的”社会成员。
现代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范例----香港没有关税或其他对国际贸易的限制(除了美国和其他一些大国施加的一些“自愿”限制外)。那里不存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指导,没有最低工资条例,没有固定价格。居民自由自在,想向谁买就向谁买,想把东西卖给谁就卖给谁,想怎么投资就怎么投资,想雇什么人就雇什么人,想给什么人干活就给什么人干活。
政府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主要是履行我们上面所说的四项义务,而且它对这四项义务 进行非常狭义的解释。它实施法律,维持秩序,提供制定行为准则的手段,裁决争端,方便 交通运输,以及监督货币的发行。它为从中国去的难民提供公共住房。虽然香港政府的开支 随着经济的增长也有所增加,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属于世界最低之列。因而,低 税保持了刺激。工商业者既可以因成功而获利,又必须为失败付出代价。
我们的社会是我们自己建立的。我们可以改变各种制度。物质的和人的特性限制了我们选择的余地。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这些都阻止不了我们去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它主要依靠自愿的合作来组织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它维护并扩大人类的自由,把政府活动限制在应有的范围内,使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让它变成我们的主人。
附录:柬埔寨大屠杀
本文中提到的「最近柬埔寨的经验悲剧性地说明,完全不要市场,会使人们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的背景就是红色高棉上台实行一系列激进的共产主义制度。
红色高棉大屠杀(高棉语:ហាយនភាពខ្មែរ / ការប្រល័យពូជសាសន៍ខ្មែរ,罗马化:Hayonphap Khmer / Karbraly Pouchsasa Khmer),或称红色高棉种族灭绝、赤柬大屠杀、柬埔寨大屠杀或柬埔寨种族灭绝(法语:Génocide cambodgien;英语:Cambodian genocide),亦被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官方称作波尔布特种族灭绝制度[1][2](越南语:Chế độ diệt chủng Pol Pot),是指1975年至1979年初,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共产主义政权在柬埔寨进行的大规模杀戮事件。据各方估计,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柬埔寨全国范围内共有150万至300万人非正常死亡,约占当时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一直以来,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本人的大力支持和援助,同时受到了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斯大林主义等的较大影响。据学者统计,中国的援助占红色高棉总外援的至少90%,仅在1975年,中方就向红色高棉提供了至少10亿美元的无息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2000万美元的“礼物”。1975年4月,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取得实权后,开始激进推行共产主义,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接见了波尔布特,而1976年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等人还亲自访问柬埔寨进行了“指导”并表示肯定。红色高棉试图创建一个农业社会主义的社会,故强迫城市人口全部迁移到乡下,并效仿中国实行“大跃进(Maha lout ploh)”,导致大量人死于疾病、过度劳动或营养不良。同时,波尔布特等人宣称要“洗净平民”,因而开始杀戮;自1976年起,波尔布特又认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于是开始了对柬埔寨共产党内部人员的大清洗,中央高层领导以及军队总参谋部几乎被屠杀殆尽,1978年仅在柬埔寨东部地区就有十万干部和军人被杀。法国学者让·拉库尔特发明“自我屠杀”一词来形容红色高棉。
由于酷刑、大量处决、强迫劳动和营养不良,造成了将近当时25%人口(约200万人)的死亡,其中有约40万人被柬共当作革命敌人杀害、死于各省的监狱之中;屠杀人口中包括了20-30万华人、占柬埔寨华人总人数的一半,此外25万伊斯兰教徒中有9万人死亡,而2万越南裔人则全部死亡。1978年,红色高棉在越南境内进行了巴祝大屠杀,导致了柬越战争激化,1979年初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被推翻、大屠杀结束。此后,各方在柬埔寨全国境内发现了超过两百个万人坑,这些地方后来被人称为“杀戮战场”。考虑到红色高棉的统治时间之短,其造成的死亡人数因此成为世界历史上最高纪录之一。1980年起,原S-21集中营被改建成了纪念大屠杀的吐斯廉屠杀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1952年起,波尔布特多次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军政训练(譬如游击队训练)以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等。1965年11月-1966年2月,波尔布特访问中国,中共高层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波尔布特讲述了“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枪杆子里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共产国际”等理论。他还会见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以及彭真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康生等人则向他介绍了一套铲除内奸的“理论”。
1970年,朗诺等人发动了政变、建立亲美的高棉共和国,西哈努克流亡中国,与此同时波尔布特跟随北越总理范文同访华。在中国共产党的协调下,红色高棉转而宣布支持西哈努克,中国是军事物品的主要供应者,仅在1970年,中国运往柬埔寨的军用物资就达400吨,卡车50辆。1974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西哈努克和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英萨利,谈到了柬埔寨解放后的政权建设问题,并且对红色高棉的方针表示赞成。
1975年6月21日,波尔布特访问中国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亲自向他传授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波尔布特推荐了姚文元写于1974年的两篇文章——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此后还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毛泽东认为:
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波尔布特则对毛泽东说:
毛主席同我们谈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带战略性的问题。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你的话去做。我从年轻时起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有关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导了我们全党。
另一方面,对于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实行的激进共产主义路线,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75年8月26日在医院会见即将返回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以及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英萨利等人,提醒到: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曾经犯过错误,我们必须为此造成的后果负责。我冒昧地提醒你们,不要期望通过一场大跃进就能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必须小心谨慎,明智行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共产主义道路。你们现在的目标不应当是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而应当缓慢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果你们抛弃这种审慎和共产主义的常识,那只能给你们的人民带来灾难。共产主义应当意味着人民的幸福、繁荣、尊严和自由。如果有人不顾人民的思想水准和民族现实,想一步就完全共产主义化,那无疑是冒险把国家和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我提醒你们不要再犯中国同样的错误。
据学者统计,仅在1975年,中方就向红色高棉提供了至少10亿美元的无息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2000万美元其它“礼物”。红色高棉统治的柬埔寨几乎完全依靠中国的物资、技术和专家的帮助才得以生存,中方人员帮助柬埔寨重建工厂、修复基础设施,同时也提供了军事援助。有学者估计,在红色高棉获得的外国援助中,中国提供的至少占90%。
附录:知乎用户Canicularis有关红色高棉和黑木崖势力的想法
171.在广东土改时期,华侨们因为通常拥有较多的现金资产,便成为了运动中的重点斗争对象。
在开平县平原乡,华侨吴奕悟因为夜间出门大便前没有打报告,就被找到理由进行了一番“斗争”,并被罚款5000万元。
结果工作队一看她这么容易就答应了交钱,就又暗示群众继续斗争,要再罚出1亿元。群众们便又对她进行了一番“猛烈斗争”,导致她在次日因伤重不治而亡。
另一位老华侨谭裔柏,在美国做了四十多年的洗衣工。年老落叶归根,返乡在家耕种着八斗田,一直到1949年时因为年老体衰,才将土地出租收了两斗谷,结果就被算了1100万的“剥削帐”。
这个老华侨之后因为害怕再遭清算,便在次年以74岁高龄重新去了美国,走的时候发誓再不寄一个钱回国。———《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东土地改革研究》
159.红色高棉中央常委的一张合影照片,从左至右分别为波尔布特、农谢、英沙利、宋先和藩蒙,以及一辆奔驰轿车。很显然,在全国范围与资本主义进行战斗的同时,并不妨碍领导人继续乘坐资本主义的豪华轿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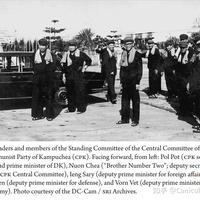
147.有一年春耕季节,恰好有一个赶集的日子,许多农民不下田去赶集,使得驻村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员极为愤怒。而去赶集的人中恰好有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地主,尽管老地主早就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但是路线教育工作队还是认定是老地主煽动农民去赶集,破坏春耕生产。到第二天晚上,生产大队召开大会批斗老地主,老地主站在大队礼堂舞台的一角接受批判,中途老地主支撑不住,由地主的儿子代替他站在台上接受了一个多小时的批判 (由于老地主身体不好,平常对四类分子的训话和劳役大多数由他的儿子代替,而这种做法在当年的农村相当普遍,以至于中共中央的一个文件中曾经批评这种作法)。批判老地主的效果显著,农民的出工率迅速上升。其实在集体化的年代,农民对集体生产并没有积极性,不出工而去赶集与老地主完全无关,工作队只是拿老地主来杀鸡吓猴,因此这件事情给笔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级初探》.李若建
138.作为红色高棉领域的权威专家之一,Ben Kiernan的这本著作是目前对红色高棉在1975-1978年统治时期描述最为详尽的著作。在其五百多页的内容中,通过对成百上千位幸存者的采访,为读者们勾画出了这个恐怖政权的真实面目——在其统治下,有近170万柬埔寨人死于非命,其中一半是被该政权直接杀害,其余的则是死于超负荷的强迫劳动与严苛的食物配给。
这期间不仅是柬埔寨境内如华裔、越南裔、占婆裔等少数民族遭受了巨大的苦难,那些被认为是红色高棉政权基石的“旧人”,既贫困的高棉族农民也遭受到了同等的对待。尤其是在1978年初开始武装反抗红色高棉的东部地区,当地的平民更是遭到了该政权灭绝性的屠杀。
在书中作者还驳斥了将红色高棉视作一场来自底层农民反抗的传统观点,事实上红色高棉的中高层领导几乎全部出自该国在战后培养出的精英知识分子。就和之前的同类运动一样,柬埔寨的农民在其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境地——他们在内战时期被动员起来成为了红色高棉的主要兵力来源,这一时期农民与红色高棉之间还保持了较为融洽的关系。
但在进入金边之后,政府就立刻转变了对待农民的立场,原本的乡村社会被打破,农民的财产与自由遭到侵犯,所有的劳动力都被集中起来进行各类强迫劳动——这一切都是为了红色高棉的“宏大愿景”而必要的牺牲。当时间走到1978年时,即便是曾经最忠诚的农民群体也开始仇恨红色高棉。而随着越南军队的入侵,在各地都发生了农民向干部复仇的群体性行为,而已经落败的红色高棉军队也不忘对农民进行报复性的屠杀,这也象征着一场更为漫长的内战即将降临这片土地。
137.“上世纪大跃进时期,潮汕有谣曲这样唱:得罪干部上兴梅,得罪炊事食淖糜”。上兴宁和梅县客区干什么?大炼钢铁呀;淖糜又是什么?极稀的粥呀。那时食堂的炊事就有这权力,同样一勺子稀饭,分量不会少你的,可稠淖全凭他的好恶。在那会饿死人的年代,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潮菜天下》.张新民
136.随着韩桑林等人于1978年在东部专区发动了针对红色高棉中央的叛乱,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也进入了最恐怖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屠杀对象已经不再是某些特定人群,而是针对整个东部专区的平民,红色高棉将该地区上百万的平民都视作叛徒,并且发动了灭绝性的大屠杀。
当时在首都金边,一位华人亲眼目睹了红色高棉将城中6000多名来自东部专区的平民驱赶上了三条轮船,然后当船行驶到湄公河中时立刻向其开火并击沉了这三条船,船上的6000多人全部遇难,流出的鲜血染红了整条湄公河。
这位华人之后又与7000多人一起乘火车被送到了西北的菩萨省。等火车一到目的地,车上就有3000多人被红色高棉的士兵当场杀死。他能够幸免于难多亏了他的华人血统,那些士兵向他解释他们不想伤害华人,只是不得不杀掉那些来自东部的旧人。
当时还有一位生活在菩萨省的占婆裔妇女也回忆道,在1978年中旬时,她所在合作社被送来了3000多名东部专区的平民。在一开始这些人就被按年龄分成了不同的组进行劳动。而在过了两个月后,大屠杀开始了,这些人被按照年龄依次带去处决。本地干部告知她东部专区的所有人都已经“病态”了,他们必须将这些人全部清洗干净。在这三千多人中只有一个百来人的小组因为被安排的工作地点偏远而幸存了下来,直到越南军队解放了本地。
另一位当时生活在巴坎的人回忆,当时有700多位来自东部的平民被安插在了他的合作社。他打听到这是因为据说东部的人都在盼望越南人的到来。很快这七百多人就在一天夜间被集体枪杀,尸体被丢进了早已准备好的沙坑,其中一些受了伤暂时还没死去的人也一起被活埋了。
一位在1975年从金边被疏散到豆蔻山脉的人也供述道,在1978年上半年有许多来自东部的人被安置在了附近的各个合作社。本地的红色高棉士兵将这些人全部视作叛徒,几乎每天都会随机拣选一些人带出去处决。在经过了四个月的杀戮后,仅有极少数的妇女与儿童幸存了下来,因为越南军队在那时已经推翻了红色高棉的统治。
此人还亲眼目睹了一次大规模杀戮,当时有一千多名来自东部的平民被蓄意安置在了一处没有水源的山地。在饥渴的驱使下,这些人不得不冒险下山向士兵们哀求给他们更换一处地方。结果士兵们直接向着人群开火,当场就射杀了数百名平民,接下去人们用了几乎一整夜的时间清理尸体,那些暂时没有死去的人又被红色高棉的士兵用刀子砍死,他们身上的衣服被剥下分给了其他平民,然后尸体赤条条的被扔进了沟渠中。
一位生活在马德望的妇女也证实道,从1978年年初开始,就不断有来自东部的平民被安置到本地。红色高棉公开的说法是越南人正在炮击东部地区,造成了当地的粮食短缺。但在私底下,士兵告诉她这些人全是不值得信任的“叛徒”。
在一开始,红色高棉会带走家庭中的男性,宣称说要集中到另一个地方进行集体劳动,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回来。然后过了两个多月,红色高棉又告知那些妇女,让她们收拾东西准备与他们的丈夫和父亲团聚,但事实上这些妇女都被牛车带去了本地的一处仓库,然后在里面被用斧子和棍棒处决。
附录:知乎文章《“太行经验”指导下的山东土改》
来源:知乎用户Canicularis
1947年中旬,随着战争的白热化,各根据地的土改工作也被要求增加强度。之前土改不够坚决的山东遭到了华东局的严厉斥责,被批判为“富农路线”、“在执行方法上是限制群众路线”。
为了指导山东进行正确的土地改革,华东局在7月7日下达了名为《关于山东土改复查的新指示》,指示中要求在之后的土改复查中“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提出要“根据90%的农民的意见行事,如果党的规定与90%农民的要求不符合,就修改党的规定”,其眼下之意就是给出了10%的“地富分子”指标以供斗争。同时还介绍了兄弟解放区的“先进经验”,既之前太行区土改杀人、扫地出门的经验。
而随着这份指示传达到基层,更是变成了“地主一切都是非法不合理的……实行扫地出门,贫雇农小组成立与整理了农会,就要真正当起家来,不能把当家成了空话,一切照百分之九十农民的意见要求行事,对地主有生杀予夺之权,任何人不能干涉。”
在这样的指示下,许多干部就理解为之前减租减息是向地主“要粮”、土地改革是向地主“要地”,而土改复查就是向地主“要命”了。而被动员起来的农村“积极分子”们,更是直接将杀人当成了唯一的考核标准。很多村庄为了争功、得奖旗、受表扬,就开始挖空心思抓特务,扫地主、挖蒋根拔蒋毛,开会动员时“不是棍子会就是杀人会。而由于山东许多地区都属于根据地,大部分地主在经历了减租减息之后土地已经所剩无几,即便全部斗争了也拿不出多少用来“动员”,因此各地就以“抓特务”的名义开始乱捕乱杀。
由于死刑权被下发到村,各地都发生许多既荒唐与可怖的现象:在莒南县大店区,据当时的一位民兵庄某回忆:
“地主家有很多官服,农教会长穿上官愿坐堂,严重的时候枕木一敲,“给我把耳朵割了!”说用刺刀截就戳死了,死了好几百口子……我那时当民兵,负责从村里往北河带人,把人带去就回来,我不敢看。会开了些日子,白天开,晚上点上汽灯开。在牟家官庄杀很多庄家地主,外边小庄子里有50亩地的也得斗,瘸子里拔将军不是?
没地的破落地主也得杀。有很多是因为自己认为没罪恶没跑就被杀了。牟家官的庄惠顿有百十亩地,假装成医生跑了。他老妈妈在家.这个老妈妈平时谁家生小孩,就今天送小米,明天送面,后天送几个鸡蛋。村里开斗争会,村干部想砸死她,说他没炮的儿子都砸死了,还剩下她吗?让大家提意见,有个人说俺媳妇生娃的时候她送这送那。干部就说:“你坐下吧,还有谁提意见?”
刘家岭村的农教会长回忆道:
……张政务在会上讲了个例子,侍家宅子村有一家弟兄6个,都当石匠,三年盖了三层炮楼,全家四十亩地……瘸子里拔将军选出来了,弟兄6个大人被砸死,小孩被一劈两半……
历家寨村农救会长回忆道:
当时我记得村里地主就三五户,一复查就扩大了……47年我当农会主席,区里开反特复查大会,村里由我和老支书参加……会场上就打死好几个,有一个瘦巴的老头。
散会了回去,回来继续开会,开会就砸,那次五X虎的二儿当兵,要回来当天就砸死了。砸死了好几个,也有砸伤的,极左的,老妈妈、小孩齐上阵。五X虎是全区开大会打死的。除了五X虎爷俩,还有个老妈妈被打了,说她有钱,没拿出来,没打死。还有两家死了俩,枪毙两个,打死了三个。贫雇农当家作登的不轻了,有天晚上有个村有个别人说XX人不好,就乱棍打死了。
在日照县芦山区的三庄村,在动员后立刻就在村中发现了一个“特务机关”,村民郑全西只因从小在西安上学,又恰好从西安回来,即被认为是国民党员,当他闻讯带着全家逃跑时,就被敢去封门的人在家门外乱棍打死。
在另一个村,因为一个被关押的“特务”乘着看守睡觉逃跑了,于是第二天村里的贫农团就将村中的一个疯子与他的儿子一并打死交账。
大坡庄回去立刻成立了“贫雇农小组”,在研究后将八户人家扫地出门,有三个还没有打死押起来了,群众说“打不打不要紧了”,但干部却不罢休,开始“商讨如何打死好”。其中一个当过曾经顽乡长的人,被一再逼问是否有政治问题,最后被迫“供出”曾干过国民党后,就“拉出去揍死了”。然后又拉出去五个斗争,也不管招供不招供,参加诉苦会的一人一根把棍子,又拿出铁锨、撅头,一哄而上打死了。在追浮财时除了吊打之外,还把一些人绑在扁担上,并残忍地放在火上烤其胳膊窝来逼其说出钱财藏在哪里,为了让地主家妇女说出浮财,就把人往鏊子上烙(鏊子是当地做烙饼的工具),又刺手指。
滨海地委委员、民运部长在1947年11月28日的滨海地委扩大会议上检讨反特复查时说:“我们普遍杀,小孩也杀大人也杀,有的一个庄杀到四五十个,如大土山杀了四十多。”当时还有个村子,只因一个疯子说有特务支部、小组,即打死了28名所谓的特务,然后就连这个疯子自己也命丧棍棒之下。
孔家口子村因荣军人孔贤美联合村民反对有贪污行为的“村老虎”村长,两者产生矛盾。荣军人当民兵的弟弟偷了一口刀去找正在区里的村长而被搞起刑讯时说他哥是特务,这位荣军人随即被抓捕。送到区公所后被打得说胡话,咬了二十余人,结果这个只有80户人家的村子就抓出了43户特务。荣军人被打死后全村又被打死11人,其他也几乎被打死,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中贫农,只几家地主富农。事后群众反映打死的十一户中,只有三个该死。其余都是屈死的。
上大峪村一开始搞出一家特务,最后却咬上了60家特务,上古崖村也咬出60多家特务。沈瞳区南鲍瞳村一个中农只因他之前的外号叫“皇帝”,分区干部听到后即不问青红皂白把他给斗了,结果全村其他四十余户中农都吓得不敢过日子。
莒南县长、县委委员高风林在1948年滨海区的土地会议上也曾说过个乱攀咬的例子,当时潘沙沟48户人家,有45被咬成了特务,党员也没能幸免了。
官庄乡召开农代会议,在会上决定打死32个所谓的地主特务,民兵带着大棍把人押到这所谓的“乡农民法庭”,审问之后就拉出去枪决了。在这次会议后下面也有样学样,高家沟村原来只打算打死一个,回去后一次就打死十一人。台庄村竟然“光选些小孩做法官”,各村都照样子学,干部一见面就互相问“您庄打死几个?
在这种为了杀人而开设的法庭下,芦山区一口气就打死了160多人,该区南部的四个乡顿时觉得自己落后了,也纷纷表态一定会“限期完成”。
望海区尧王城村,由于一批物资丢失,乡长看谁都像特务,于是就听了一个流氓的话,把该村在外逃难刚来家的五个老实村民扣押起来,乡长带头前后审讯了三次,期间有一个农民竟然被活活吓死。
到了八月后,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进逼,各地的基层干部也开始惶惶不安起来,生怕遭到报复,于是就产生了“一网打尽满河的鱼”的想法,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之前许多只是稍有嫌疑的人,都统统打死了事。
芦山区的区委书记马吉德当时听说城里地主反攻倒算得厉害,于是就决定北边四个乡先打死105人,凡是地主即全部打死。之后随着战事紧急,许多之前被扣押的人被干部视作况累赘和负担,因此就把所有与敌伪有联系的、特务地主的妻儿、伪保长、流氓等等一概打死,声称“上次打死男人,这次打死女人,总之是能打死的一定打死。”
三庄村之前分两批打死了10个所谓的特务地主、封建地主。还有一些流氓坏分子“群众”本来也要打死,在干部劝说后暂时留下了,但在这次则全打死了,全村前后打死20人,上吊投井7人。望海区的区公所把附近100多个地主富农押了户虎睡岭,在林子里第一天挑了11个杀了,第二天又杀了6个。
黄墩区的梁山乡,其前前后后也一共打死了45人,外加送到县里枪决的10余名“特务”,也足足杀了五六十人,但还是被认为“落后了”。
当时在日照县巨峰区马瞳村,有一位村民名叫丁立现,他的父亲早年就死了,母亲顶着女地主的身份领着一家人勉强度日。四七年夏天时因为国民党军队进逼,全村的人都奉命向着河南边躲避。期间他母亲因为裹了小脚走得慢,结果到河边时就被干部摁到河里给灌死了,她的两个闺女见状扑上去想去救母亲,结果也被一道摁到水里灌死了。
后来丁立现四处找他老娘,结果被那位凶手威胁说“连你弄进去!”而他的母亲和两个姐姐并不是仅有的受害者,当时全庄有34个人都因为类似的原因被杀害。
巨峰分区的委员袁培瑞,在他同另一乡的干部交换意见说你乡打死多少他就打死多少。该乡石桥官庄一夜打死十二人,即是他强令打死的。在他带领下口要杀人都由干部小组长动的手。干部又下命令,谁不砸就与地主同罪,杀人的时候全村硬逼出五十余人开会,干部动员说“不砸死,来了敌人不和咱一条心,留一个一个刺眼钉。”还举例子说“崖头打死得多立功”指导员李克楷说,“咱敢不敢?”下边说“敢”就这样拉出打死了。
当时望海区有一位颇有名望的士绅名叫郑振东,他他创办过新式学校,积极投身于抗日活动,日照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还被选为县参议员。但在斗地主时由于当地强调按政策办事,这样一位爱国士绅即被害死了。芦山区三庄乡范家楼范聚东是当时著名的开明士绅,知书达理,抱有极强烈的爱国热忱,在抗日战争期间倾力支持中共抗日,为中共党和军队输送了大批的青年才俊,他生活居住的村庄范家楼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小延安”。但就是这样一位著名人士,仅仅因为在村里得罪了极少数人而在土改复查中被报复打死,而他那位已经做了藏马县农会主席的儿子范熙彭却爱莫能助,唯一所能作的即是“来信脱胎换骨,不承认父亲。”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清下,神经紧张的村民几乎看到任何陌生人都有特务嫌疑。当时有人走路者带了匣枪,就被捉去即以特务罪名打,有区队到石墩送信,虽然互相都认识却因无路条被打”。秦滩井村一妇女说“如割韭菜,一茬一茬,早晚挨着了。
在斩草除根的思想驱使下,有些地区只要家中有人涉嫌与国民党有联系,就会将其全家杀害。芦山区官庄乡高家沟打死的十一人里有两户为贫农,这两家老小一共被打死六口。之后村干部又怕其在区中队的两个儿子报复,威胁要带回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区干不同意,乃逼其二人表明态度才放过。大坡村通过刑讯逼供使一村民假供自己是国民党并咬上其他庄的几个人,当场有人说“这些人国民党来了不会与咱一心,非打死不行”,于是连他一共五个人一上场,群众一拥而上乱棍打死。该村一村民只因其儿在国民党当兵,“群众怕,即砸死了”。
由于胡乱攀咬成风,许多干部自身也成了受害者。滩井乡林家滩井村中的党员本就分为两派,当时一个被押地主咬上了其中一派的农会会长就三青团成员,另一派的干部就立刻将其逮捕,计划将其兄弟打死,后经区干发现方才救了这位农会长一命。
在当时,村民之间任何微小的嫌隙都会演变成杀戮。巨峰区马庄乡崖头村的农会主席只因自家小孩与组织出夫有功的村团长的小孩打架,即“主持要斗他,组织了十九个出夫开小差者将他打了,喊着要枪决,幸乡长知道禁止”,但这位村团长仍被“扫地出门”。石桥官庄李克枯与李茂父同为贫雇农,只因争山场时被李克枯争去,李茂父怀恨在心而乘开会之际呼口号:“这是正式坏蛋”,就这样李克枯在会场上被打死了。
沙沟村原村干郑培延因与村民郑培夫的母亲不睦,就诬称郑培夫散布谣言说“中央军进攻啦”,开会时非要将其弟兄四个都砸死,并威胁村干不能阻止“群众翻身”。在斗的时候,只郑培延自己提了一个意见,马上持一口大刀即杀了二口,当夜共杀了九口。接着郑培延追问群众:“彻底不彻底?”群众反映差不多了,但郑培延说:“不彻底啊”这样群众害怕了,还不知道要杀多少。第二天早晨去检尸跑了一个(郑培夫之五弟)但还是被上河提回又杀了。
附录:知乎回答波梗好笑在哪里?
来源:知乎用户Canicularis
最好笑的就是简中互联网上部分群体针对这段历史的超高强度造谣,他们大概是想用这种信息污染的方法来扭曲这段历史:
谣言一:
看到了金边有两百万人,但是认为只要柬埔寨向大国磕头就可以拿到粮食了。
事实:柬埔寨不需要磕头也拿到了粮食,红色高棉四月占领金边,而外国的粮食援助就五月就已经送到,外国势力还贴心的送上了包括衣服、药品、农药、铁路设备、燃料等等一切用于维系国际运作的物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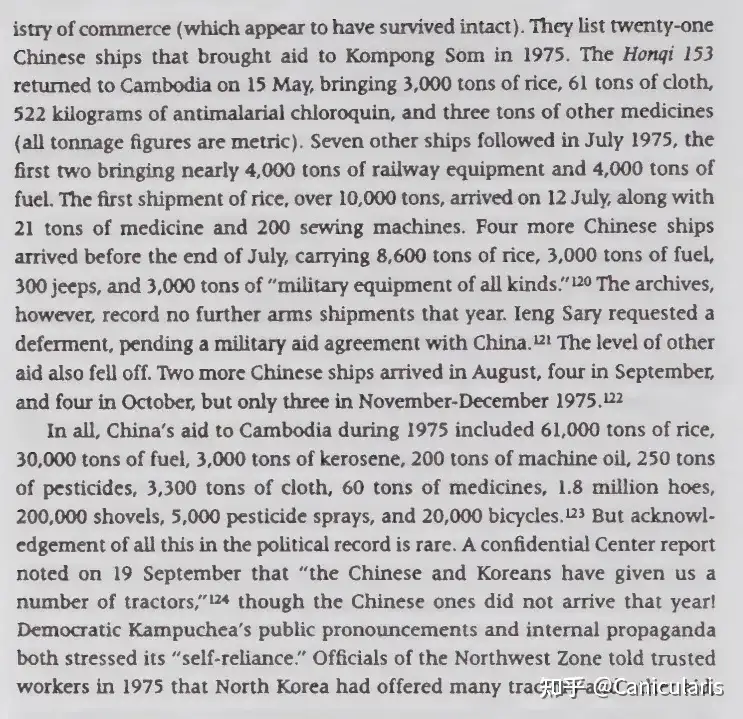
谣言二:
无视金边两百万人挤在一起,真切的认为波波去城市化是为了搞原始主义
事实:波尔布特早在占领金边之前就已经制定了清空柬埔寨全国城镇的计划,这并非只是针对金边,凡是能称得上镇子的居民点都被清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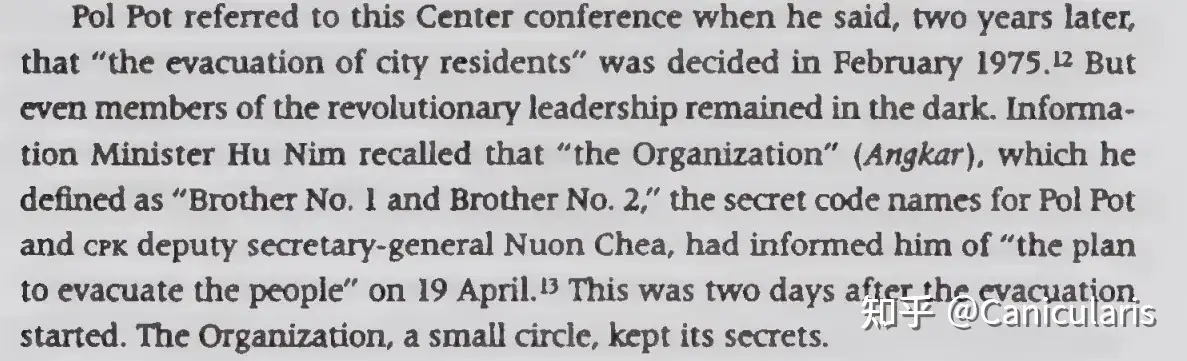
谣言三:
觉得只要波波不去袭击越南就不会打起来,在中越边境跳腾的黎笋在对柬埔寨问题上居然能如此冷静,难道柬埔寨比我们还厉害?
事实:是柬埔寨主动在1977年初挑起了对越战争,并对越南领土上的柬埔寨难民与越南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才让越南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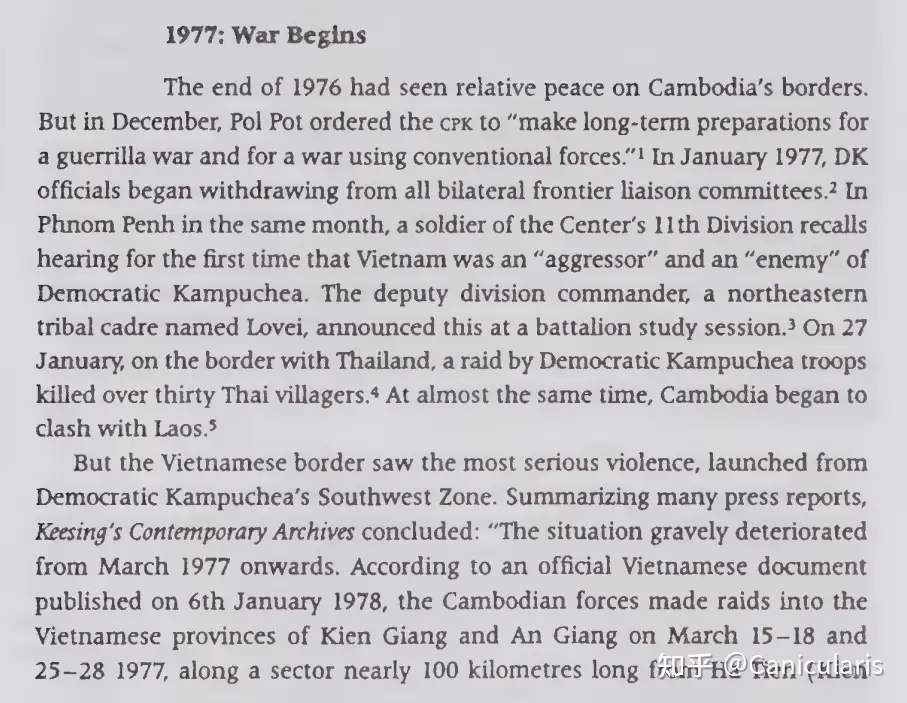
谣言四:
4.自由党国际成员,柬埔寨烛光党(救国党)至今仍在给波波辩护,认为这是越南人制造的谎言。
事实:这个谣言是红色高棉在被越南人赶出金边后为自己辩护而散播的,但S-21的主官康克由在2009年接受国际法庭审判时就特意反驳了这条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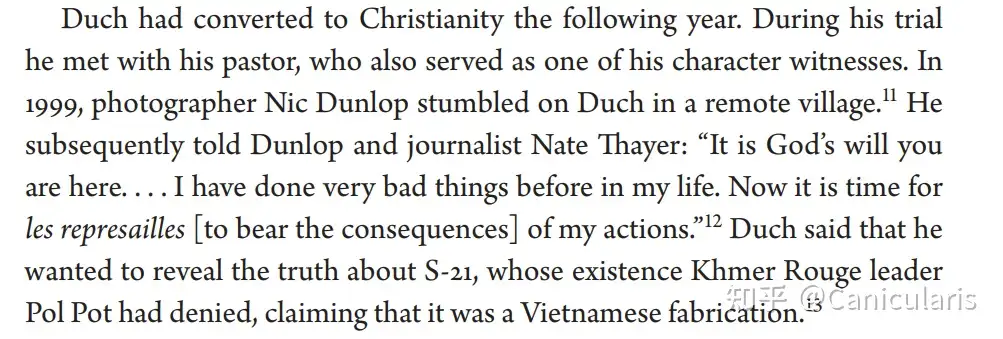
谣言五:
两百万的出处居然是电视剧《第五共和国》里车智澈说的,我愿称之为虫豸计数法
事实:这段话属于是在自曝其丑。学术界对红色高棉在1975-1979统治全国期间造成的死亡人数认定是170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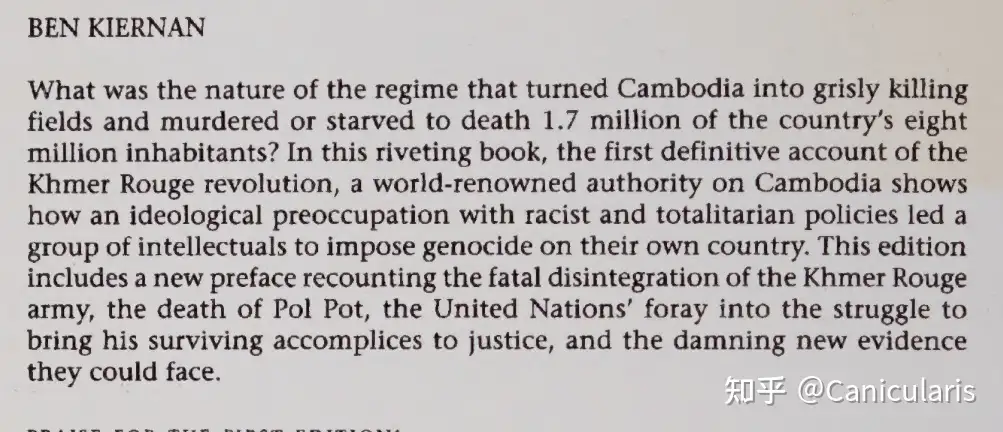
谣言六:
韩桑林也参与了图图,但是没人骂他。
事实:有大量的证人可以证明,韩桑林所属东部专区的是当时纪律最为严格,也最人性化的武装力量,早在红色高棉用暴力驱逐金边市民时,就发生过多次这支部队为了保护民众而与红色高棉的嫡系部队发生冲突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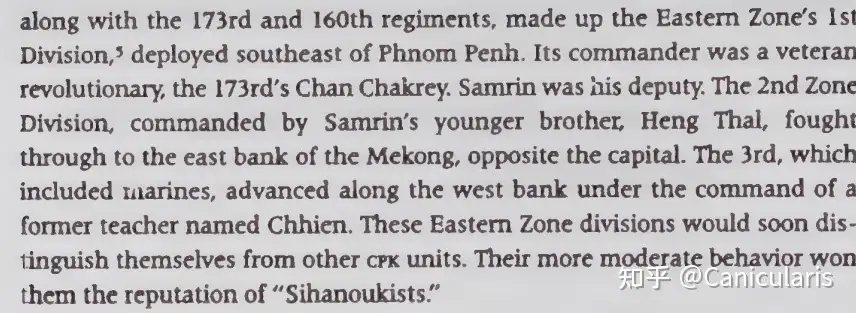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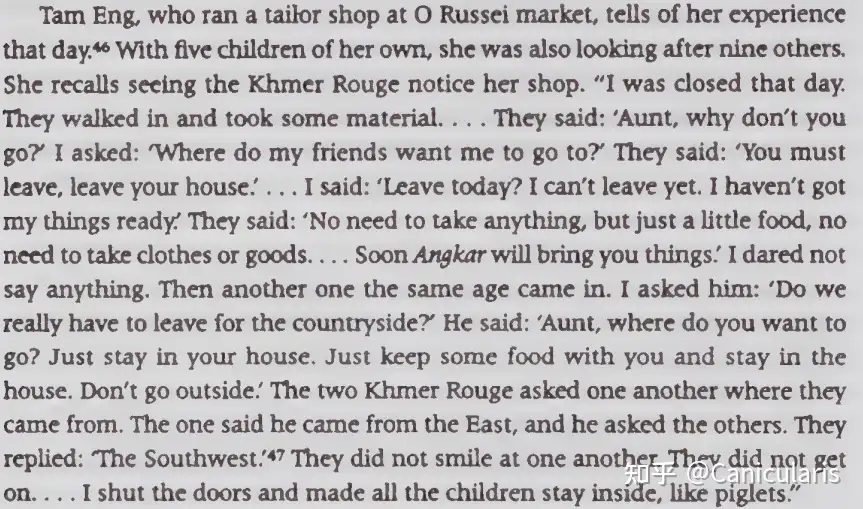
附录:俄国人的劣根性
《财富、贫穷与政治》第3章<文化因素>信任与诚实
尽管信任能促成对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合作方式,但信任如果缺乏诚信必定是一场灾难。一个社会的诚实度框定了这个社会的信任半径,造成的经济影响超过许多有形优势。
例如,苏联即便不是地球上自然资源最富集的国家,至少也是其中之一。苏联也是仅有的工业国中石油储量极其丰富的国家,甚至是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国之一。它土壤肥沃, 享有盛名,并且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平原。102苏联的铁矿石储量也是世界第一,森林覆盖面积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拥有世界第二大锰储量103和世界三分之一的天然气储量104。 除此之外,在许多年里,苏联作为镍生产国也领先于世界105。在几乎所有自然资源上, 苏联都能自给自足,并且出口了大量的黄金和钻石。到1978年,全世界接近一半的工业级钻石都是由苏联生产的。106
然而,根据两位苏联经济学家的研究,虽然苏联拥有这些有形的自然资源优势,民众也接受了良好教育,苏联的经济在效率上却远远不如德国、日本或美国。107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欧、美国或日本,而日本是世界上资源最匮乏的国家之一。
如此受自然青睐的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平为何会低于许多自然资源不如它的国家呢?苏联的存在简直就是为了反驳地理决定论。抵消苏联在自然方面优势的其他影响因素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文化方面的。回到19世纪,当苏联还被称作沙皇俄国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针对阻碍其经济发展的文化障碍是这样评价的:
官员普遍贪污腐败,这制约了沙皇俄国的经济发展能力:因为官员的报酬取决于他们能否成功地让人们的烦恼翻倍,这样人们才会为免除烦恼向他们行贿。108
腐败带给经济体的成本不只是行贿的金钱或被官员窃取的钱物,甚至主要不是这些。 最主要的成本是没有发生的事——没有开始的商业活动、没有进行的投资和没有发放的贷款。在一个极其腐败的经济体中,这些经济活动的回报率必须高于个人的努力成果不容易被剥夺的经济体,这样人们才会去做。
19世纪晚期,沙皇政府试图让俄国经济更加现代化,并邀请西方企业来俄国开展商业活动,这些企业会雇用俄罗斯人做工人,慢慢也会雇用俄罗斯人做管理者,但他们从不雇用俄罗斯人做会计。不只俄罗斯人当会计是个问题,20世纪初的一位法国观察家曾友好地指出,俄罗斯人当管理者在经营中也会造成非常多的浪费。109在俄罗斯,“像德国人一样诚实”和“像德国人一样守时”110曾是常用语,表明俄罗斯人自身很少具备这些品质。 过去的文化差异到了今天为什么是这样的,又是如何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会迷失在时间里,但这类文化品质对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
普遍的腐败在俄罗斯延续了下来,甚至在斯大林统治下也存在。尽管有诸多惩罚——包括遭受劳工集中营的奴役。苏联经济中有一群被称作“中介者”(tolkachi)的人,他们主要为企业从事非法活动,这些企业在官方许可的有限活动中受到严格限制,很难完成莫斯科的中央计划制定者给他们设定的目标。111
在沙皇俄国时期普遍存在的腐败在整个苏联时期都没有消失,也延续到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一家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股价仅相当于美国同类石油公司股价的1%,因为“市场 预期俄罗斯石油公司会受到内部人士有组织的劫掠”。112根据一家俄国报纸的报道,要想被一些声誉卓著的高等院校录取,需要行贿1万到1.5万美元。据该报估计,每年俄罗斯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的此类支出至少有20亿美元。
俄罗斯以其自然资源富集和生活水平低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113,告诉我们有形因素的优势如何被不利的无形因素制造的障碍所抵消。当然类似情况不只发生在俄罗斯一国。普遍的腐败使得开发自然资源所需的大额投资风险过高,结果就是不论本地还 是外国投资者都不愿意冒险一试。
但是在其他情形下,信任半径能让某些特殊群体富裕起来,而且不只是在繁荣的国家,很多是在法律体系不可靠又腐败的第三世界国家。一些群体如印度的马尔瓦尔人或东南亚 华人中的小群体,即使没有合约或不具有主流社会的法律或政治制度,他们也可以彼此从事金融交易。在正式的法律体系无效或腐败的国家,这是一种独特的优势。因为它给予了 群体成员更大的信任半径,使得相对于群体外部的人,他们的经济决策更快捷,风险也更小。
在更发达的经济体中,特定群体内部的高信任度同样是一种优势。例如,纽约的哈西德派犹太人根据口头协议寄售昂贵的珠宝,并基于非正式协议共享收益。114印度的马尔 瓦尔人在国际贸易网络中也这样做115,东南亚华人的小群体也有同样的现象116。另外, 西非和西半球部分地区的黎巴嫩人小群体也有类似的贸易模式。117
《财富、贫穷与政治》第3章<文化因素>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很重要,它不仅能够在物质资本遭受毁灭性破坏后帮助一国迅速恢复,例如战后重建;它在正常年代的经济进步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我们与穴居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力资本。
有些人倾向于将人力资本等同于教育。毫无疑问,教育是人力资本的一种,我们也经常粗略地用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但应当指出的是,许多人力资本是在学校之外获得的,此外一些学校教给学生的技能很多不是市场需要的,个别学校还会以负面态度、错误预期和厌恶之情等形式产生负人力资本,对经济产生不好的影响,因而学校对学生人力资本的开发贡献很少,甚至为零。鉴于教学内容不同,教育有时会让人对进入私人部门工作产生反感,或拒绝从事任何不满足“有意义的工作”这一定义的事,这里的“有意义”是指那些能够让人心满意足的工作。
开创工业革命的人大多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他们都是有实际工作技能和经验的人,而非精通科学的科学家或系统研究过工程的工程师。在正式的科技研究普及之前,工业革命已经在进行中了。甚至后来的工业先驱如托马斯·爱迪生和亨利·福特接受的正式教育也很少,怀特兄弟高中就退学了。到了电子时代,比尔·盖茨和迈克尔·戴尔均是大学肄业生。总之,人力资本不等同于正式的学校教育。
人力资本可以表现为教育之外的其他形式,教育普及也不意味着同样的人力资本普及。 21世纪的俄罗斯被称作“高教育水平和低人力资本的社会”122。从更直接的经济角度看, 俄罗斯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口大约占全世界的6%,但在全世界新专利和专利申请量中仅占0. 2%。1995年到2008年间,德国、日本和美国发明的专利大约分别是俄罗斯的60倍、200倍 和500倍,甚至新加坡这样的小城邦国家的发明专利也比俄罗斯多。123
附录:魁奈对斯密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家对儒家有误解,其实儒家反而影响和启发过西方
对于自然形成的市场秩序,最佳状态是应该不加干涉,即“善者因之”,其次才是进行引导和教导,“最下者与之争”,最糟糕的情况便是朝廷去与民争利,其实是批评当时的盐铁垄断和均输政策,其态度与贤良文学是一致的。过去一些主张自由市场的西方经济学家对儒家的经济思想有误解,如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就认为,儒家与法家接近,而老庄才主张自由经济的,鲍芝(David Boaz)也认为,老子是第一个自由经济的主张者。但实际上,随着认识的深入,已经有西方经济学家指出,根据《论语》《孟子》以及《盐铁论》等文献中反映的儒家思想,恰恰是主张自由经济和商业传统的(Roderick T.Long;Austro-Libertarian themes in early Confucianism.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Volume 17,no.3(Summer 2003),PP35—60)。
可以说,儒家思想的经济底色既不贬低商业活动,更不是主张“抑商”,而是尊重市场的基本自然法则,体现为“无为”。这一思想,在近代传播到欧洲,并对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的法国重农学派曾产生过积极影响。如魁奈(Francois Quesnay)就曾通过西卢埃特受到过“中国哲学家的书籍”影响,并且颇为崇尚儒家思想,而西卢埃特是在1687年从孔子的著作中获取到了关于“听从自然的劝告”,“自然本身就能做成各种事情”的观点,由此联想到以天道观念为基础的中国“无为”思想,有助于对西方自然法的研究。英国学者赫德森认为魁奈的自然秩序思想就是中国主张君主“无为”的观念,日本学者泷本诚一认为法国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观念与中国思想相同,我国学者侯家驹也曾指出“我国儒家经济思想启发了西方自由经济思想”。谈敏先生认为,儒家主张的无为,以治理为目的,尤其讲究德治,这对于魁奈当时正在积极寻求一种新的经济原则,以此取代他所坚定反对的国家干预型重商主义政策来说,显然产生了很大启迪作用。综合考察来看,“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原则,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儒家的无为思想之变形”(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212—214页)。
附录【李竞恒】《儒家的商业观,和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古老的商业文化,重视财富
商业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周易·系辞下》记载说在遥远的神农氏时代,就出现了原始的市场,“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商人”“商业”词汇的来源,便是擅长经商的商民族,《尚书·酒诰》说商民族的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他们驾驶着牛车到远方经商,赚钱孝养自己的父母。商民族的祖先首领王亥、王恒等人,也是擅长经商的,《周易》大壮、旅卦分别提到他们“丧羊于易”“丧牛于易”,赶着牛羊四处经商,遭到有易部落的袭击而丧生。部族首领亲自经商,甚至为此而死,说明商民族有重视商业活动的传统。商代金文族徽中,有些是人背贝串的图像,代表了以贸易为职业的氏族,以商贸为族徽,也显示了商业具有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三联,1999,第382页)。商亡国后,商王畿地区的遗民仍然擅长经商,如殷遗民的聚居中心洛阳,在周代发展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的商人“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遍布各地,十分活跃。在一般民间,如原商王畿的卫国,商业活动也活跃,人们熟悉的《诗经·卫风·氓》,就描写当时卫地民间“抱布贸丝”的商业活动,而著名的儒商子贡也出生于卫,当是受到此种风俗的熏染。
孔子为殷人后裔,应当也对商业文化并不陌生,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孔子反复说“沽”,使用商人的语言,说明他对市场非常熟悉(余英时:《商业文化与中国传统》)。和一般人想象的陈腐穷老头形象不同,孔子本人并不敌视商业活动和富贵,他认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富有是值得追求的,所反对的只是“不义而富且贵”,而“富而好礼”(《学而》),则是他最赞赏的模式。《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曾笑着对爱徒颜回说:“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希望颜回能够富有,自己来担任其管家。这也可以解释孔子对其爱徒子贡的态度,他将儒商子贡比喻为“瑚琏之器”这样的宗庙宝物(《论语·公冶长》),而不是将其批评为“满身铜臭的财主”,就很能说明原始儒学对于商业活动与财富的基本态度。
重视契约的传统,有时甚至拯救国家
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契约传统,但西周的郑国在立国时代,便和商人们建立起一项宪法性的契约,所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左传·昭公十六年》),意思是只要你们商人不背叛国家,那么国家就保证不强买你们的商品,也不会强行索取或抢夺。你们有怎样的巨额财富,都与国家无关。这一契约,在日后对保护郑国商人财产权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两百年后,势力强大的晋国权臣韩宣子向郑国商人索要一件玉环,郑国执政官子产以“这不是国家府库收藏的器物”为理由回绝了。韩宣子又用压价的方式,向商人强行购买玉环。这时,子产搬出了两百年前的这项契约,谈到了商人与国家的约定,国家有义务保护商人的财产权,否则“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最后,韩宣子只能放弃强买的打算。
子产坚持了郑国的古老契约,守护了商人财产,他能“养民”的德性,受到了孔子的高度评价,认为他是“惠人也”(《宪问》),“其养民也惠”(《公冶长》)。郑国有保护商业和财产权的契约传统,因此商人地位较高,也愿意维护国家的利益。最著名的便是弦高犒师的典故,公元前627年,郑国商人弦高到成周去经商,在滑国遇到了要偷袭郑国的秦军,为了保护郑国,他急中生智假冒郑国使者,用自己的十二头牛犒劳秦军,并派人回国报信防备,秦军认为郑国已有准备,便放弃了偷袭计划。
《左传·成公三年》记载,晋国的大臣知罃在邲之战中被楚国俘虏,有“郑贾人”试图将他藏在要贩运的丝绵“褚”中带走逃离,但还未行动,楚国人就将知罃放回去了。知罃想报答这位郑国商人,商人却说“吾无其功”,因为知罃是楚国人放的,自己没帮上忙,便拒绝了赏赐,又到齐国去做生意。从这里也可看出,郑国商人很讲究诚信,讲究无功不受禄。此外,他们经常参与国际间的政治活动,也说明社会地位不低,有一定道义和理想的观念。显然,只有长期生活在一个财产得到良好保护的社会,才会养成这样的品德和趣味,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
先秦时期的儒家,有时也以商业契约的思维,来比喻和理解君臣关系。例如清华大学收藏竹简的儒书《治政之道》中,就提出了“君臣之相事,譬之犹市贾之交易,则有利焉”(《文物》2019.9)。意思是,君臣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和商业交易相似的契约关系,臣带着礼物“质”寻找合作的君,双方达成合作契约,便通过“委质为臣”,建立起契约关系。通过契约合作,让君臣双方都获得受益。
孟子的商业思想,与亚当·斯密相通
到了战国时代,孟子对商业和市场也持开放态度。在《孟子·梁惠王下》,他提出治国需要“关市讥而不征”(在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在《尽心下》中,他提出“古者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意思是古代建立关隘,是为了保护社会,而不是为了多收税,他主张对民间商业不收关隘税。这一点与英国《大宪章》第13条,免除各市、区、镇、港的关卡税,皆享有免费通关权的主张是一致的(《大宪章》,商务印书馆,2016,第33页)。战国时期各国设立有很多的关卡收税,如包山楚简《集箸》简149就记载了七个邑、四个水道日常要收取“关金”,但是从战国时代的鄂君启节铭文来看,像鄂君启这样的特权贵族来说,又可以沿途关卡免税,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孟子的主张就是,各个关卡,无论贵族还是普通商人,都统统不收税,藏富于民。所以梁启超先生对这一主张的评价是:“儒家言生计,不采干涉主义”(《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90页)。孟子认为,只要能更好地保护民间商业,就会“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孟子·梁惠王上》),天下的商人都希望来这个低税率的国家,市场则会进一步繁荣。
孟子的另一项关于社会分工的思想,也是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哈耶克曾谈到,远古以来的人无法理解商业活动的实质。他们看到商业“贱买贵卖”,因此将其视为一种可怕的魔法。西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对商人表示藐视(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科出版社,2011,第101—102页)。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的原始儒学这里,就没有这种偏见,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对商业活动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而非蔑视。当时有神农家的许行,反对社会分工,带领其弟子自己耕田、打草鞋和织席子(《滕文公上》),对此孟子的态度是,既然许行戴的帽子、耕作用的铁农具,都是用自己种的粮食交换而来,那就说明了社会分工的必然性,没必要事必亲为,这也正是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合理性。许行还认为,理想状态是市场上所有商品价格相等,轻重相等的丝绸和麻布也都价格等同,就会实现社会正义。
孟子针对这种人为干预市场价格的谬论,提出这是乱天下的观点,如果大鞋和小鞋子都同一个价格,谁还去生产大鞋子?可以说,儒者孟子是为自由市场辩护的,而那位反对社会分工,主张干预价格的许行,根据钱穆先生考证,是南方楚地的墨家,禽滑厘的弟子(《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2,第408—409页)。
即使是战国晚期,出现了荀子这种比较法家化的儒者,也仍然重视市场分工和贸易的优势。《荀子·王制》中强调,中原地区能够得到北海的走马吠犬,南海地区的羽毛、象牙,东海地区的鱼、盐和染料,西海地区的皮革。水边的人能获得足够的木材,山上的人能得到足够多的鱼,农民不用冶炼能获得足够的农具,工匠不用亲自耕田却能获得足够的粮食,“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能产生这样神奇效果的,只能是充分发育的市场贸易和社会分工。
抑制和打击商业是秦朝和法家文化
在诸子百家中,儒学对商业和市场的态度最为肯定,而最为敌视商业和市场的则是法家。《商君书·弱民》提出弱民的主张,主张“利出一孔”,只有为君主耕战才能获取利益,而民间若能通过经商致富,即所谓“商贾之可以富家也”(《农战》),显然会削弱“利出一孔”的机制,民间便可以“皆以避农战”,不会为君主所用。在《垦令》篇中,商鞅将商人视为“辟淫游惰之民”,要“赋而重使之”,达到“商劳”的效果。主张“商贾少,则上不费粟”,认为商业活动是消耗了社会资源,要达到“商怯,则欲农”,“商欲农,则草必垦”,另一方面加重关口的税率,“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逼迫商人成为耕战之民。同样,韩非子对商业也极其敌视,他认为“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将工商业者视为可恶的游民,要让他们身份卑贱,因为商人“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韩非子·五蠹》),经商致富会破坏耕战的吸引力,削弱“利出一孔”的制度。
秦国坚持法家重农抑商的耕战政策,导致秦国几乎没有出现著名的大商人,如吕不韦是来自东方,并非秦人,而且在秦国的身份也只是参与政治,而非商人。又如《史记·货殖列传》中出现的两位“秦国大商人”乌氏倮、寡妇清,其实也并非秦人,而是属于受到政策优待的边境少数民族。乌氏倮是甘肃戎狄游牧部落的商人,通过给戎狄王送礼而得到便利,因而发财致富。巴寡妇清是西南巴族豪酋的子孙,经营祖传的丹砂矿致富,能“用财自卫”,即当地拥有部落武力的豪族,并非秦国的编户齐民。秦始皇为其筑怀清台,并非是重视商业,而只是笼络边境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权术而已。秦始皇对商人的真实态度是敌视的,在秦《琅邪刻石》中,他就吹嘘自己“上农除末”,即尊崇农业,打击了末业(商业),这才是秦皇真实的想法。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后附录有收入秦律的《魏奔命律》,其中提到对“假(贾)门逆旅”即商人和开客店者的仇视,要将他们全部抓到前线当炮灰,吃犯人的伙食,“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壕”(《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第294页),拿这些商人和店老板去填壕沟,当炮灰。
整个秦朝,儒家、商业社会都遭受重创。岳麓书院收藏秦简《金布律》中,规定“禁贾人毋得以牡马、牝马高五尺五寸以上者载以贾人市及为人就载,犯令者,赀各二甲,没入县官马”(陈长松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年,第110页),不允许商人使用高头大马经商,否则没收马匹并重罚款。此外,《金布律》规定,商贾如果在大路上做买卖,就会被“没入其卖也于县官”,当然,官府卖东西,则“不用此律”。刘邦集团继承了秦的基本遗产,继续执行“抑商”的政策,“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盐铁论·本议》),降低商人的政治地位。《史记·平准书》记载,“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不但用重税打击商人,并且规定商人子孙不得当官,不能乘坐马车和穿丝绸。应该说,汉代国家继承了秦朝的基本政治遗产和治理观念,所不同的是,汉初经济凋敝,又部分吸取了亡秦的教训,而官方的道法家思想虽然和纯法家思想之间具有共同渊源,但却更加灵活,可以在不全面启动秦制的前提下实行部分“无为”,以启动民间巨大的经济创造力。
到汉武帝时期,汉朝重新启动半休息状态的秦制,打击商人以汲取财富。元朔二年,强制将天下“訾三百万以上”的富商迁徙到茂陵,进行控制(《汉书·武帝纪》);另一方面是垄断盐铁经营,“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史记·平准书》),经过桑弘羊将其直属于大司农,进行全国性的垄断;并且实行酒类的国家专卖,“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汉书·武帝纪》);此外又对商人收取算缗的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两千钱就要上交一百二十钱作为财产税,其后又鼓励告缗,如果商人不如实登记和上缴财产税,有人告发,就可以获得该富商的一半财产。2013年在成都老官山西汉墓葬M1中出土的木牍,记载有“贾皆没入所不占”,“令诸郡国贾”等文字,正是对商人进行管制和打击的记录(《考古》2014.7),整理者认为这批简牍文书内容与汉武帝的算缗、告缗政策有密切关系(《考古》2016.5)。严酷的告缗打击,导致当时一半中产以上的人家破产(《史记·平准书》)。著名的铁器大商人卓氏家族、程氏家族,在西汉中期以后便没有相关的记载了,很可能便是在武帝的盐铁和算缗打击下,走向了衰败和灭亡。武帝死前将负责盐铁垄断的桑弘羊作为精心安排的托孤之臣,后来实际上仍然继续执行武帝的时政方针(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北京三联,2015,第27—28页)。
汉朝官营工厂效率低下,儒者主张“盐铁皆归于民”
面对此一困境,儒家士人的态度是反对此类抑商政策。早在武帝刚实行盐铁政策不久,儒者董仲舒就主张“盐铁皆归于民”,“薄赋敛”,将盐铁经营还给民间商人,并减少过高的赋税(《汉书·食货志上》)。在昭帝始元六年的盐铁辩论会议上,主要以儒家士人为主的“贤良文学”站在民间立场,高度反对武帝遗留下来的盐铁政策。主张盐铁垄断的官僚们赞美商鞅,垄断了山泽大川的利益,实现了“国富民强”。相同的道理,盐铁垄断也是“有益于国”的。贤良文学们则反驳,汉文帝时没有盐铁垄断,而民间富裕,而现在则导致了“百姓困乏”(《盐铁论·非鞅》);主张垄断的官僚们认为民营盐铁的商人是“不轨之民”,如果一旦“利归于下”,保障了民间能获取利益,就会“县官无可为者”。针对此说,贤良文学们强调“公刘好货,居者有积,行者有囊”(《盐铁论·取下》),强调古代的贤王从来不会与民争利。他们还指出,官府垄断的铁器生产,质量低劣,“县官鼓铸铁器……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盐铁论·水旱》),官府役使大量卒徒生产,这些被役使的劳动力也不会尽心,保证产品质量。官府生产的烂农具,价格还定得特别高,导致很多农民只能“木耕手耨”,用木头耕土,用手薅草。
汉代官府垄断导致铁器品质低劣,这也得到了考古资料的证实,居延汉简记录,铁官所造武器,弩口有伤洞,釜口缺漏。连军用铁器的质量尚且如此,当时农具的品质可以想象得到。而尹湾汉墓出土的木牍《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中,则记载了数量颇为巨大的库存武器,仅仅是一个东海郡的武库,就藏有五十三万多件弩、上千万的箭矢、十四万件甲、九万八千件盔、四十五万件铍、九万九千把剑等数量极其巨大,可以武装上百万人的武器。一个东海郡,显然并不需要这么巨大数量的武器。如此众多的闲置武器,也可以窥见官府铁器生产的规模甚巨,有庞大的生产计划,所谓“务应员程”,即“计其人及日数为功程”(《汉书·尹翁归传》颜师古注),但产品却是质量低劣,一般铁器不能卖出,只能“颇赋与民”,强行摊派,掠夺民间。而武器装备,则堆山填海地储存在各地武库中。最新考古资料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2017年在山东青岛土山屯147号西汉晚期墓出土木牍记载,元寿二年,一个小小的堂邑县,就储存了二十七万三千多件武器,而其中竟多达三万二千多件都存在质量问题,需要“可缮”(《考古学报》2019.3)。从这些迹象都能看出,汉朝官铁垄断的效率和质量非常低下。
针对官营盐铁的低效和扰民,贤良文学们强调了以家族为纽带的民营效率:“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盐铁论·水旱》),民营的家族企业,家人们同心协力,能够制作高质量的商品,品质低劣的产品根本无法流入竞争充分的市场。此外,贤良文学提出,“王者务本不作末”,“是以百姓务本而不营于末”,“天子不言多少”,看起来好像是看不起“末业”和赚钱,但其实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所反对的是朝廷垄断的“末业”,而非民间。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贤良文学此处真正所反对的,不是民间工商业,而是以盐铁、均输等重大措施,由朝廷直接经营的工商业。”(《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大学版社,2002,第86页)。
虽然盐铁论战未能战胜与民争利的制度垄断,但儒者有理有据地展现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到东汉儒学更进一步发展后,他们坚持的努力终于起到了效果。章和二年四月,朝廷下诏书,“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后汉书·和帝纪》),废除了盐铁垄断的制度,允许民间商业自由参与,这正是多年来儒者与社会一起努力的结果。
司马迁赞美商业和“素封”,是儒道合一的文化背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学者司马迁对商业的积极态度。可能一些人会说,司马迁不是儒家,而是道家或杂家。实际上,司马迁的学术虽然确有百家驳杂的色彩,但却又以儒学为基本底色。徐复观先生认为“他以儒家为主,同时网罗百家”(《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194页),应该是很准确的归纳。《汉书·司马迁传》说他“年十岁则诵古文”,清代学者王先谦注释说“史公从安国问”,意思是司马迁从小就跟随大儒孔安国,学习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先秦儒书。他关于《春秋》的知识则是“余闻之董生”,就是跟随大儒董仲舒学习《春秋》,后来他写《史记》也是模仿作《春秋》。在学术训练和知识传承上,受业于两位儒学名家,以儒学作为底色。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将孔子尊奉到诸侯级别的“世家”,并评论“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他将孔子尊为至圣,正是儒者背景的体现。周德伟先生曾谈到:“吾人须知司马迁乃儒学正统,孔子之大成至圣地位,即由彼所确定,其所言点点均符合孔子及以后圣哲之教……圣哲何尝不重视经济因素及人民之利。但反对以政治手段干涉经济势力的自然发展,则以司马迁表现得最明朗”(《周德伟论哈耶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4—165页)。
作为以为儒学为根基的学者,司马迁对商业和市场的态度与《盐铁论》中的贤良文学们相似。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并赞美了大量优秀商人和家族企业,如范蠡、白圭、倚顿、邯郸郭纵、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宣曲任氏、韦家栗氏等,他赞美儒商子贡,能通过巨大的财富和社会影响力“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子贡对儒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司马迁甚至发明了一个词汇“素封”,就像将并没有实际王位,但却行有王者之事的孔子被尊为“素王”一样,优秀的商人和企业家被他尊为“素封”。他指出,工商业和社会分工是必须的,而这一切会自然形成,所谓“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人们为了牟利,便会竭尽所能,参与市场分工。自由的市场一旦形成,便会“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社会变得繁荣。“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他的意思是,农民生产粮食,虞人运输物流,工人将原材料制作为产品,商人把产品四处贩卖,这些市场分工是自发形成的,根本不需要官府事先通过人为设计把他们配置在一起。根据自由市场的规律,价格的波动自然调配商品流动,就像水一样日夜不息地自然流淌,不用强制的行政命令,市场自然会将产品送到消费者面前。
西方经济学家对儒家有误解,其实儒家反而影响和启发过西方
对于自然形成的市场秩序,最佳状态是应该不加干涉,即“善者因之”,其次才是进行引导和教导,“最下者与之争”,最糟糕的情况便是朝廷去与民争利,其实是批评当时的盐铁垄断和均输政策,其态度与贤良文学是一致的。过去一些主张自由市场的西方经济学家对儒家的经济思想有误解,如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就认为,儒家与法家接近,而老庄才主张自由经济的,鲍芝(David Boaz)也认为,老子是第一个自由经济的主张者。但实际上,随着认识的深入,已经有西方经济学家指出,根据《论语》《孟子》以及《盐铁论》等文献中反映的儒家思想,恰恰是主张自由经济和商业传统的(Roderick T.Long;Austro-Libertarian themes in early Confucianism.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Volume 17,no.3(Summer 2003),PP35—60)。
可以说,儒家思想的经济底色既不贬低商业活动,更不是主张“抑商”,而是尊重市场的基本自然法则,体现为“无为”。这一思想,在近代传播到欧洲,并对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的法国重农学派曾产生过积极影响。如魁奈(Francois Quesnay)就曾通过西卢埃特受到过“中国哲学家的书籍”影响,并且颇为崇尚儒家思想,而西卢埃特是在1687年从孔子的著作中获取到了关于“听从自然的劝告”,“自然本身就能做成各种事情”的观点,由此联想到以天道观念为基础的中国“无为”思想,有助于对西方自然法的研究。英国学者赫德森认为魁奈的自然秩序思想就是中国主张君主“无为”的观念,日本学者泷本诚一认为法国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观念与中国思想相同,我国学者侯家驹也曾指出“我国儒家经济思想启发了西方自由经济思想”。谈敏先生认为,儒家主张的无为,以治理为目的,尤其讲究德治,这对于魁奈当时正在积极寻求一种新的经济原则,以此取代他所坚定反对的国家干预型重商主义政策来说,显然产生了很大启迪作用。综合考察来看,“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原则,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儒家的无为思想之变形”(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212—214页)。
附录:弗朗索瓦·魁奈
弗朗索瓦·魁奈(法语:François Quesnay,法语:[fʁɑ̃swa kɛnɛ],1694年6月4日—1774年12月16日),法国经济学家,重农主义的领袖、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先驱。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1]。
魁奈早年以行医为生,后在任路易十五宫廷御医时开始研究经济学。
1758年魁奈写出著名的《经济表》,他用图表来说明社会各经济阶级和部门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它们之间支付的流通,并提出了经济平衡的假说。
他提倡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该思想——甚或名字——很可能来自中国无为哲学的启发[2][3])。
魁奈对中国的经济有所研究,曾著有《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
魁奈更提出“纯产品学说”,他认为物质才是财富,唯有农业才能使财富增加,而工业只能改变财富的形态,不能增加财富的数量,服务业更不能增加财富的数量。并进一步提出“土地单一税理论”,也就是说既然农业创造出纯产品,所以他主张只对土地的收入征缴税收。
后来的李克洲认为,魁奈的经济思想,来源于他所处的时代。为此,李克洲对魁奈提出“纯产品学说”的解释为:“魁奈时代的法国,农业中已经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在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发展起来,还是由小业主性质的生产经营占据主导地位。”
可见因为魁奈所处的农业社会环境,当时的确存在“纯产品”(利润)这种现象,但是在工业社会中,这种观念就不存在了。
因此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在重农学派本身得出的结论中,对土地所有权的表面上的推崇,也就变成了对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上的否定和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肯定”。
因此,在农业中,存在“纯产品”(利润),而在工业中,就不存在“纯产品”(利润)。但魁奈由于没有所有权决定价值的思想,因此他错误地认为,“纯产品”来自自然的恩惠。
虽然时空背景如此,但是他很得亚当斯密的尊重。
亚当斯密曾在1764年至1766年间和他的弟子一同游览欧洲,大多是在法国,在那里斯密也认识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英。
魁奈身为重农主义学派的领导人,斯密极为尊重他的理论。但是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一书,就否定了重农主义学派对于土地的重视,相反的,斯密认为劳动才是最重要的,而劳动分工将能大量的提升生产效率。
参考文献
Derk Bodde. CHINESE IDEAS IN THE WEST (PDF). ASIAN TOPICS IN WORLD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2005 [2015-04-08].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4-10-09).
1 Source (PDF). [2008-03-04].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08-03-07).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John M. Hobson, p.196
附录François Quesnay
François Quesnay (French: [fʁɑ̃swa kɛnɛ]; 4 June 1694 – 16 December 1774) was a French economist and physician of the Physiocratic school.[1] He is known for publishing the "Tableau économique" (Economic Table) in 1758, which provide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ideas of the Physiocrats.[2] This was perhaps the first work attempting to describe the workings of the economy in an analytical way, and as such can be viewed as one of the fir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thought. His Le Despotisme de la Chine, written in 1767, describes Chinese politics and society, and his own political support for enlightened despotism.[3]
Life
Quesnay was born at Méré near Versailles, the son of an advocate and small landed proprietor. Apprenticed at the age of sixteen to a surgeon, he soon went to Paris, studied medicine and surgery there, and, having qualified as a master-surgeon, settled down to practice at Mantes. In 1737 he was appointed perpetual secretary of the academy of surgery founded by François Gigot de la Peyronie, and became surgeon in ordinary to King Louis XV. In 1744 he graduated as a doctor of medicine; he became the physician in ordinary to the king, and afterwards his first consulting physician, and was installed in the Palace of Versailles. His apartments were on the entresol, whence the Réunions de l'entresol[clarification needed] received their name. Louis XV esteemed Quesnay highly, and used to call him his thinker. When he ennobled him he gave him for arms three flowers of the pansy[4] (derived from pensée, in French meaning thought), with the Latin motto Propter cogitationem mentis.[5]
He now devoted himself principally to economic studies, taking no part in the court intrigues which were perpetually going on around him. Around 1750 he became acquainted with Jacques C. M. V. de Gournay (1712–1759), who was also an earnest inquirer in the economic field; and round these two distinguished men was gradually formed the philosophic sect of the Économistes, or, as for distinction's sake they were afterwards called, the Physiocrates. The most remarkable men in this group of disciples were the elder Mirabeau (author of L'Ami des hommes, 1756–60, and Philosophie rurale, 1763), Nicolas Baudeau (Introduction a la philosophie économique, 1771), Guillaume-François Le Trosne (De l'ordre social, 1777), André Morellet (best known by his controversy with Galiani on the freedom of the grain trade during the Flour War), Lemercier de La Rivière, and du Pont de Nemours. Adam Smith, during his stay on the continent with the young Duke of Buccleuch in 1764–1766, spent some time in Paris, where he made the acquaintance of Quesnay and some of his followers; he paid a high tribute to their scientific services in his Wealth of Nations.[6][4]
Quesnay was married in 1718 to a woman named Marianne Woodsen, and had a son and a daughter; his grandson by the former was a member of the first Legislative Assembly. He died on 16 December 1774, having lived long enough to see his great pupil, 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Baron de Laune, in office as minister of finance.[4]
Works
His economic writings are collected in the 2nd vol. of the Principaux économistes, published by Guillaumin, Paris, with preface and notes by Eugène Daire; also his Oeuvres économiques et philosophiques were collec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 by August Oncken (Frankfort, 1888); a facsimile reprint of the Tableau économique, from the original MS., was published by the British Economic Association (London, 1895). His other writings were the article "Évidence" in the Encyclopédie, and Recherches sur l'évidence des vérites geometriques, with a Projet de nouveaux éléments de géometrie, 1773. Quesnay's Eloge was pronounced in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by Grandjean de Fouchy (see the Recueil of that Academy, 1774, p. 134). See also F.J. Marmontel, Mémoires; Mémoires de Mme. du Hausset; H. Higgs, The Physiocrats (London, 1897).[4]
Economics
In 1758 he published the Tableau économique (Economic Table), which provide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ideas of the Physiocrats. This was perhaps the first work to attempt to describe the workings of the economy in an analytical way, and as such can be viewed as one of the fir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thought.[7]
The publications in which Quesnay expounded his system were the following: two articles, on "Fermiers" (Farmers) and on "Grains", in the Encyclopédie of Diderot and Jean le Rond d'Alembert (1756, 1757);[8][4] a discourse on the law of nature in the Physiocratie of Dupont de Nemours (1768); Maximes générales de gouvernement economique d'un royaume agricole (1758), and the simultaneously published Tableau économique avec son explication, ou extrait des économies royales de Sully (with the celebrated motto, Pauvres paysans, pauvre royaume; pauvre royaume, pauvre roi); Dialogue sur le commerce et les travaux des artisans; and other minor pieces.[4]
The Tableau économique, though on account of its dryness and abstract form it met with little general favor, may be considered the principal manifesto of the school. It was regarded by the followers of Quesnay as entitled to a place amongst the foremost products of human wisdom, and is named by the elder Mirabeau, in a passage quoted by Adam Smith,[6] as one of the three great inventions which have contributed most to the stability of political societies, the other two being those of writing and of money. Its object was to exhibit by means of certain formulas the way in which the products of agriculture, which is the only source of wealth, would in a state of perfect liberty be distributed among the several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namely, the productive classes of the proprietors and cultivators of land, and the unproductive class composed of manufacturers and merchants), and to represent by other formulas the modes of distribution which take place under systems of Governmental restraint and regulation, with the evil results arising to the whole society from different degrees of such violations of the natural order. It follows from Quesnay's theoretic views that the one thing deserving the solicitude of the practical economist and the statesman is the increase of the net product; and he infers also what Smith afterwards affirmed, on not quite the same ground, that the interest of the landowner is strictly and indissolubly connected with the general interest of the society. A small edition de luxe of this work, with other pieces, was printed in 1758 in the Palace of Versailles under the king's immediate supervision, some of the sheets, it is said, having been pulled by the royal hand. Already in 1767 the book had disappeared from circulation, and no copy of it is now procurable; but, the substance of it has been preserved in the Ami des hommes of Mirabeau, and the Physiocratie of Dupont de Nemours.[4]
Orientalism and China
Quesnay is known for his writings on Chinese politics and society. His book Le Despotisme de la Chine, written in 1767, describes his views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system.[3] He was supportive of the meritocratic concept of giving scholars political power, without the cumbersome aristocracy that characterized French politics, and the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e to the welfare of a nation. Gregory Blue writes that Quesnay "praised China as a constitutional despotism and openly advocated the adoption of Chinese institutions, including a standardized system of taxation and universal education." Blue speculates that this may have influenced the 1793 establishment of the Permanent Settlement in Bengal by the British Empire.[9] Quesnay's interests in Orientalism has also been a source of criticism. Carol Blum, in her book Strength in Numbers on 18th century France, labels Quesnay an "apologist for Oriental despotism."[10]
Because of his admiration of Confucianism, Quesnay's followers bestowed him with the title "Confucius of Europe."[11] Quesnay's infatuation for Chinese culture, as described by Jesuits, led him to persuade the son of Louis XV to mirror the "plowing of sacred land" by the Chinese emperor to symbolize the link between government and agriculture.[12]
On Taxation
Quesnay acknowledged three economic classes in France: the "proprietary" class consisting of only landowners, the "productive" class of agricultural workers, and the "sterile" class of merchants. Quesnay saw no benefit to the sterile class and believed the productive to be all important. Quesnay viewed France's agriculture as backward and unproductive compared to Britain during the time he was residing in the Palace of Versailles [13] . Despite residing in the Palace, Quesnay believed agriculture was the heart of the economy and of special importance to him. Quesnay argued that taxes placed on cultivators are only harmful to society as these taxes will reduce the incentive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axing proprietors (property holders) does not destroy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meaning there is no decline in output. Quesnay wanted proprietors to bear the full burden of the tax in the country as taxing cultivators is a negative consequence for everyone. Removing incentive from cultivators reduce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agricultural surplus Quesnay believed to be the heart of the economy [14]. Quesnay also opposed indirect taxes in contrast to direct taxes. These "indirect taxes" are placed on the French public by proprietors whose greed demands immunity from taxation. Direct taxes on proprietors has no impact on reproduction and economic decline [14]. Reducing indirect taxes and increasing direct taxes gives the French a surplus of agriculture and the funding the country needs. However, this opinion was not very popular among the wealthy of which Quesnay spent time regularly with. He spent some of his time fearing for his life in the Palace.
See also
Contributions to liberal theory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Liberalism
Ronald L. Meek
Circular flow of income
Notes
Cutler J. Cleveland, "Biophysical economics", Encyclopedia of Earth, Last updated: 14 September 2006.
See the biographical note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Volume 31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89) p. 605.
Ina Baghdiantz McCabe (15 July 2008). Orientalism in Early Modern France: Eurasian Trade, Exoticism and the Ancien Regime. Berg Publishers. pp. 271–72. ISBN 978-1-84520-374-0.
One or more of the preceding sentences incorporates text from a publication now in the public domain: Chisholm, Hugh, ed. (1911). "Quesnay, François".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Vol. 22 (11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742–743.
"Nouvelles Ephemerides, Économiques, Seconde Partie, Analyses, Et Critiques Raisonnées. N° Premier. Éloge Historique De M. Quesnay, Contenant L'Analyse De Ses Ouvrages, Par M. Le Cte D'A***". Taieb.net. Retrieved 16 August 2012.
Smith, Adam, 1937, The Wealth of Nations, N. Y.: Random House, p. 643; first published 1776. Phillip Anthony O'Hara (1999).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Economy. Psychology Press. p. 848. ISBN 978-0-415-18718-3. Retrieved 21 July 2012.
Kafker, Frank A.; Chouillet, Jacques (1990). "Kafker, Frank A.: Notices sur les auteurs des 17 volumes de « discours » de l'Encyclopédie (suite et fin). Recherches sur Diderot et sur l'Encyclopédie Année (1990) Volume 8 Numéro 8 p. 112". Recherches Sur Diderot et Sur l'Encyclopédie. 8 (1): 101–121.
E. S. Shaffer (30 November 2000). Comparative Criticism: Volume 22, East and Wes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39–40. ISBN 978-0-521-79072-7.
Carol Blum (5 February 2002). Strength in Numbers: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and Power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JHU Press. p. 16. ISBN 978-0-8018-6810-8.
Murray N. Rothbard (2006).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Adam Smith.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p. 366. ISBN 978-0-945466-48-2.
Geoffrey C. Gunn (2003). First Globalization: The Eurasian Exchange, 1500 to 1800. Rowman & Littlefield. p. 148. ISBN 978-0-7425-2662-4.
附录:科斯定理
知乎回答
作者:SilliySeal
科斯定理:只要产权明确,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则不管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
举个例子,有个村子在河流下游,造纸厂在河流上游,村子抱怨造纸厂污染河流,造纸厂认为河流没有归属,但谁都不愿意去买一套污水处理设备,这样僵持不下。
因为科斯定理,将河流归属给造纸厂,村民没办法只能自己掏钱装污水处理设备,这样造纸厂可以排污水,村民也不必收到污水的影响,结果是有效率的。
如果将河流归给村民,那么村民就有权利要求造纸厂要么停工要么掏钱安装污水处理设备,污水厂没办法只能装了,这样最后结果又达到了奇妙的平衡。
维基百科词条
科斯定理(英语:Coase theorem),描叙一个经济体系内部的资源配置与产出,在外部性存在的情形下,其经济效率所可能受到的影响。这个理论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1960年代的论文中提出。乔治·斯蒂格勒在1966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首次将他的见解进行归纳,并被后人称为科斯定理,事实上他不曾使用过科斯定理一词,或者定义他们可以自己解决外部性问题。
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中由罗伯特·库特对“科斯定理”的解释。他写道:“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以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
科斯是在考虑无线电广播频率时发展出科斯定理的。两家广播电台假如在同一个频段广播,便可能互相干扰,而管理者则必须将各个频段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分配给不同的广播电台,从而消除电台之间的干扰。科斯的定理认为,只要对频率的产权界定清楚,那么无论频率在初始阶段如何分配,市场最终都会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过程如下:在两家存在争议的电台之间,从争议频段中可以获得更大利益的电台甲假如对该频段没有产权,他也有足够的诱因向另一家电台乙购买或租用该频段的使用权,因为甲为了拿到频段而愿意付出的金额必定大于乙为了放弃频段而愿意接受的金额。因此,频段的初始分配会影响到两家电台的盈亏状况,却改变不了频段达到最有效率的分配状态的必然结果。
以上的情况,只有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才成立,而在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易中便会出现阻碍。比如在以上的例子当中,甲为了拿到频段而愿意出的金额当中,有一部分必须作为甲乙双方的交易成本(如谈判费、诉讼费等)被扣除,余下的数量或许就不足以为了放弃频段而愿意接受的金额,甲可能就争取不到对该频段的使用权,市场就无法达到最有效率的状况。因此,在分配产权时,分配者应该尽量减低有可能出现的交易成本,使市场参与者能够进行交易,这样市场才能够达到有效率的最终状态。
附录:外部性
在经济学中,外部性(英语:externality)或外部成本(英语:external cost)、外部效应、溢出效应,是作为另一方(或多方)活动的影响而产生的未参与第三方的间接成本或收益。 外部性可被视为涉及消费者或生产者市场交易的未定价商品。 车辆废气造成的空气污染就是一个例子。 空气污染给社会造成的代价,不是由车辆生产者或使用者向社会其他人支付的。 来自工厂的水污染是另一个例子。 所有消费者都因污染而变得更糟,但市场并没有为这种损害提供补偿。 正外部性是指个人在市场上的消费增加了他人的福祉,但个人不向第三方收取收益。 第三方本质上是获得免费产品。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可能是面包店上方的公寓,每天早上都能闻到新鲜糕点的香味。 住在公寓里的人不会为此利益补偿面包店。
外部性的概念最早是由经济学家亚瑟·塞西尔·庇古在 1920 年代提出。负外部性的典型例子是环境污染。 庇古认为,对负外部性征收等于边际损害或边际外部成本的税(后来称为“庇古税”)可用于将其发生率降低到有效水平。 随后的思想家们争论了是征税还是监管负外部性更可取、庇古税收的最佳效率水平,以及什么因素导致或加剧了负外部性,例如为公司投资者提供有限责任公司所造成的损害。
当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或消费的私人价格均衡无法反映该产品或服务对整个社会的真实成本或收益时,通常会出现外部性。这导致外部性竞争均衡不遵守帕累托效率条件。 因此,由于可以更好地分配资源,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一个例子。
外部性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 政府和机构经常采取行动将外部性内部化,因此市场定价交易可以包含与经济主体之间交易相关的所有收益和成本。最常见的做法是对这种外部性的生产者征税。 这通常类似于不征税的报价,一旦外部性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征收非常高的税。 然而,由于监管机构并不总是掌握有关外部性的所有信息(参考信息不对称),因此可能难以征收正确的税款。 一旦外部性通过征税被内部化,竞争均衡理论上会达到帕累托效率。
例如,造成空气污染的工厂制造活动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健康和清洁成本,而选择对房屋进行防火处理的个人的邻居可能会受益于降低火势蔓延到自己房屋的风险。 如果存在外部成本,例如污染,生产者可能会选择生产比要求生产者支付所有相关环境成本时生产的更多的产品。 由于自主行为的责任或后果部分在自身之外,因此涉及成本外部化(英语:Cost externalizing)因素。 如果存在外部利益,例如公共安全,则生产的商品数量可能少于生产者因他人的外部利益而获得回报的情况。 同时,从社会经济学的观点来看:
- 个人通常会倾向于“外部不经济”的消费行为,因为有害外部性商品带来的成本不需要个人承担(如污染),经济上称此为“过度消费”(英语:overconsumption)
- 而由于有益外部性商品带来的收益并不能被个人独占,个人通常在一定程度上不愿意做出“外部经济”的消费行为(如教育),经济上称此为“不充分消费”(英语:underconsumption)。
外部效应是经济决策的不平衡影响,不能归咎于决策者,因为决策者与受决策影响者之间缺乏价格或市场机制调和其利益。
一桩交易的买方或卖方如果认为结果对自己不利,那么交易不会成功,所以两愿交易被认为是对于双方都有利的;但是交易成果可能会对第三方造成额外的影响。从受到影响的第三方角度来看,这些影响可能是负面的(例如工厂排放污染),也有可能是正面的(采蜜的蜂群也会附带给邻近植物授粉)。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认为在合理条件下,外部性的存在将导致非社会最优的结果。那些遭受外部成本的人是不由自主的,而那些享受外部利益的人则不需耗费成本。
如果有外部成本存在,两愿交易可能会减少社会福利。遭受空气污染外部性影响的人将其视为自己的效用降低:主观的生气不满或自己负担的成本,例如医疗费用较高。外部性甚至可被视为危害居民的肺部,侵犯到他们的生命与财产权。因此,外部成本可能构成道德或政治上的问题;或被视为生命与财产权无法明确界定的情况,例如,排放污染到物权没有归属人的水域(象征性地为社会大众公有,或是明文在某些国家或/且法定传统上;例如禁止排放污水到溪流或海洋中)。
另一方面,正面的外部性将会增加第三方的效用,集体社会福利得到改善;而提供此外部性的私有者却无法获取其利益,即少有意愿增多生产;那么依无政府的理论模式中,集体的福利不会达到社会最优的数量。具有正面外部性的物品包括教育(被认为可提高社会的生产力和福利,尽管更高教育水平的外部性,将由更高工资率而内部化),公共卫生计划(可降低第三方的健康风险和成本,例如传染疾病)和正直的司法与执法。
正面的外部性通常与搭便车问题有关。例如,接种疫苗的人减少了周围其他人感染相关疾病的风险;在高水平的防疫措施下,社会将获得很大的健康福祉; 但任何人都有可能拒绝接种疫苗,却仍然借由“搭便车”的方式,规避掉原应支付接种疫苗的费用。
当涉及负面的外部性时,有一些提高整体社会效用的理论方法。其一是以市场驱动来纠正负面外部成本,对第三方不愿承担的成本将其“内部化”,例如要求污染者赔偿或修复排污所造成的任何损害。但在许多情况下,内部化成本或收益是不可行的,特别是无法确定造成外部性真正的货币价值。
尽管外部性不一定是轻微或局部的,自由贸易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有时将外部性称为“邻域效应”或“溢出效应”。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同样认为,外部性是因为拥有“个人财产权的明确定义”。
第2章 管理的专横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关税和对国际贸易的其他限制时,写道:
”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产业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向他们购买。“ ”在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而且必然在于,向售价最廉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这个命题是非常明白的,费心思去证明它,倒是一种滑稽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自私自利的诡辩混淆了人们的常识,这亦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在这一点上,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正相反。”
斯密的这些话,现在仍然同当时一样正确。在国内和国外的贸易中,从售价最低的地方购买物品而向出价最高的地方出售物品,是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的。然而“自私自利的诡辩”却导致出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使我们买卖什么、向谁买卖、以什么条件买卖、雇用谁或为谁工作、住在哪里以及吃什么、喝什么,总之,所有的一切都受到了限制。
亚当·斯密指责“商人和制造业者进行自私自利的诡辩”。在他那个时代,商人和制造业者可能是主要的罪人。现在他们有了许多同伙。的确,我们中间几乎没有哪个人不在这一或那一领域进行“自私自利的诡辩”。用波哥的不朽名言来说:“我们碰到了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责备“特殊利益”,但当“特殊利益”关系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就不责备了。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对自己有利的,对国家也有利——因而,我们的“特殊利益”便各不相同。
其最后结果是,各种约束和限制一起向我们涌来,使我们大家的处境如此之糟,以至如果取消所有这些限制,我们的处境反倒会好一些。为别人的“特殊利益”服务的措施给我们带来的损失远远大于为我们“特殊利益”服务的措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最明白的例子是国际贸易。某些生产者因关税或其他限制所得到的好处,抵不上给其他生产者尤其是一般消费大众造成的损失。自由贸易不仅能促进我们的物质福利,而且还能促进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协调,鼓励国内的竞争。
【按:政府决策要以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福利为依据。】
控制对外贸易会发展成控制国内贸易。它们会同经济活动的各方面交错在一起。这种控制经常受到辩护,认为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特别是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更是这样。把1867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同1947年独立后的印度作一比较,我们就能检验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和其他例子一样,这一比较说明,国内外的自由贸易是贫穷国家改善其人民生活的最好途径。
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经济控制,不仅限制了我们利用经济资源的自由,而且也影响了我们在言论、出版和信仰等方面的自由。
国际贸易
人们常说,如果经济学家意见不一致,那就一定是坏的经济政策;相反,如果所有经济学家意见一致,那就一定是好的经济政策。经济学家确实时常意见不一,但就国际贸易来说,情况却不是这样。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不管在其他问题上思想立场如何,在国际贸易这一问题上却几乎一致认为,自由贸易最符合各贸易国和整个世界的利益。可是各国都征收关税。仅有的几个较为重要的例外是:1846年废除谷物法后英国将近一个世纪的自由贸易、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三十年的自由贸易和今天香港的自由贸易。美国在整个十九世纪一直征收关税,二十世纪,特别是1930年国会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后,美国进一步提高了关税。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法案加重了大萧条的严重程度。自那时以来,通过签订一系列国际协议,关税有所削减,但目前仍然很高,也许高于十九世纪的水平。由于国际贸易中的项目种类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现在无法作精确的比较。
同以往一样,现在仍有许多人支持征收关税,并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国内工业。钢铁生产者和钢铁工人工会要求限制从日本进口钢材。电视机生产者及工会则疏通国会议员,试图用“自动协议”的办法限制从日本、台湾或香港进口电视机和电视机零件。纺织品制造商、鞋类制造商、养牛业者、制糖业者和无数其他的人也都抱怨受到了来自外国的“不公平的”竞争,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他们。当然,没有哪一个集团在赤裸裸的自我利益的基础上提出这种要求。每个集团都讲“总的利益”,讲维持就业或加强国家安全的必要性。近来,在这些传统的主张限制进口的理由之外,又增加了另外一条理由,就是需要加强美元对马克或日元的地位。
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理由
历来很少听到的是消费者的呼声。近年来,所谓消费者特殊利益集团越来越多。但是,任你查遍报章杂志或是国会作证记录,也找不到任何记载,表明他们发起过对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的集中攻击,尽管消费者是这种限制的主要受害者。我们将在第七章里看到,那些自称为消费者说话的人,关心的是别的事情。
个别消费者的呼声,在工商业者及其雇员的一片“自私自利的诡辩”的吵嚷声中被淹没了。结果是把问题严重歪曲了。例如,主张征收关税的人认为,创造就业机会本身就是一个可取的目标,不管受雇者干些什么,而且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我们需要的只是工作,我们可以创造任何数目的工作——例如,让人挖坑再填上,或者做其他无用的事。工作有时候自身就是酬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我们为取得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付出的代价。我们真正的目的不光是要有工作,而且要有生产性的工作——那些意味着将有更多的货物和劳务供消费的工作。
另外一个很少受到驳斥的谬论是,出口好,进口不好。实际远非如此。我们并不能吃、穿或享受输出的货物。相反,我们可以吃中美洲的香蕉,穿意大利的鞋,开德国的车,并在日本产的电视机上欣赏节目。我们从对外贸易中得益的是输入。出口是我们为进口付出的代价。正如亚当·斯密非常清楚地看到的那样: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能为出口换回尽可能多的进口,或者为进口支付尽可能少的出口,那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我们所使用的使人产生误解的字眼,反映了我们的一些概念性错误。“保护”实际上意味着剥削消费者。“贸易顺差”的实际意义是出口超过进口,也就是说输出货物的总值超过输入货物的总值。在自己家里,你一定愿意少付多得,而不是相反,可是在对外贸易中,这却被称作“收支逆差”。
支持关税的一个最得人心的论据,是所谓需要保护美国工人的高生活水平,使之免遭日本、韩国或香港的工人的“不公平的”竞争,因为这些工人愿意为低得多的工资工作。这个论据错在哪里,难道我们不想保护我国人民的高生活水平吗?
这个论据的错误,在于滥用“高”工资和“低”工资这些字眼。高工资和低工资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美国工人得到的是美元;日本工人得到的是日元。怎么比较以美元支付的工资和以日元支付的工资呢?一美元合多少日元,它们之间的汇率由什么来决定?
让我们来看下面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况。先假设一美元合三百六十日元。这是多年间的实际汇率。按这个汇率,假定日本人能够比我们在美国花比较少的美元生产和销售各种东西——电视机、汽车、钢铁以至大豆、小麦、牛奶和冰淇淋。如果实行国际自由贸易,我们将试图从日本购买我们的所有货物。也许这就是为关税辩护的人们所描绘的那种极端可怕的情景——日本货泛滥成灾而我们什么也卖不出去。
在吓得不知所措以前,先来进一步分析一下。我们怎样来偿付日本人呢?我们将给他们美钞。他们拿了这些钞票将干什么,我们上面假定,按三百六十日元对一美元的汇率,什么东西都是在日本便宜,因此在美国市场上,没有任何东西是他们想买的。如果日本出口商愿意把美钞烧了或是埋了,那于我们就太好了。我们可以用这些能够大量地很便宜地制造出来的绿票子换得各种货物。我们将有一种能够想得出来的最了不起的出口工业。
自然,日本人事实上不会把有用的货物卖给我们,换取无用的票子去烧掉或埋掉。他们同我们一样,想为他们的工作得到一些实在的报酬。如果按三百六十对一的汇率,所有的货物在日本比在美国便宜,出口商将试图卖出他们手中的美元,将试图按三百六十对一的比价卖掉它们,以购买便宜的日本货。但是谁愿意收购美元呢,不仅日本出口商想卖掉美元,日本的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如果三百六十日元能够在日本比一美元在美国多买到每一种东西的话,那么,没有一个人会愿意拿三百六十日元换一美元。出口商发现没有人愿意按三百六十对一的比价买进美元,就会少要一些日元。于是美元的日元牌价就会下跌——跌至三百比一,或二百五十乃至二百比一。反过来说,要购买一定数量的日元,需付越来越多的美元。日本货是以日元标价的,所以它们的美元标价会涨。反之,美国货是以美元标价的,因此,日本人用一定数额的日元得到的美元越多,对日本人来说,美国货的日元标价就越便宜。
美元的日元标价,将一直下跌到日本人从美国购买的货物的美元价格基本上等于美国从日本购买这些货物的美元价格为止。按那个价格,每个想用美元购买日元的人,都会找到愿意卖出日元换取美元的人。
自然,实际情况要比这个假设的例子复杂。参加贸易的是许多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和日本,而且贸易常采取迂回的方式。日本人可能把他们赚得的一些美元花在巴西,巴西人又把它用在德国,德国人又花在美国,总之,实际情况无比错综复杂。但原则是一样的。不管在哪个国家,人们要美元总是为了购买有用的东西,而不是为了囤积。
另外一个复杂情况是,美元和日元并不只是用于购买货物和劳务,还用来投资和送礼。整个十九世纪,美国几乎每年都有国际收支逆差,但这种贸易逆差却给每个人带来了好处。外国人想在美国投资。例如英国愿意向我们输出货物,以换取纸片——不是美钞,而是些保证过些日子连本带利偿还借款的债券。英国人愿意送货物给我们,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债券是好的投资。一般说来,他们是对的。因为同其他方法相比,他们从这种积蓄中得到的报酬比较高。而我们也得到了好处,外国投资使我们能够比完全依靠自己的积蓄发展得更快。
二十世纪,情况发生了逆转。美国的公民发现,他们向外国投资可以得到比在国内投资更高的报酬。结果,美国把货物送出国外,换取债务凭证,即债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以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援助计划的形式给外国送礼。我们把货物和劳务送给外国,以表示我们确实是在促进世界的和平。除政府的馈赠外,还有私人的礼物,如慈善团体开展的活动、教会资助的传教活动、个人对国外亲戚朋友的资助等。
这些复杂情况并不改变上述假设的极端情况所说明的结论。在现实世界里,象在假想的那个世界里一样,只要美元的日元标价或马克标价或法郎标价是在自由市场上由自愿的交易决定的,就不会发生收支差额的问题。说美国高工资工人作为一个整体会受到外国低工资工人的“不公平的”竞争,这话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自然,某一部分工人可能因为国外制造出了新产品或改进了产品或是外国生产者能够更便宜地生产某些产品,而受到损害。但这同其他美国公司制造出了新产品或改进了产品或是发现了更节省成本的生产方法而给某一部分工人带来的影响,并无区别。实际上这就是市场竞争,正是依赖于市场竞争,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才得以提高的。我们若想从一种生气蓬勃的、充满活力的、富于创造性的经济制度中得到好处,就必须认识到运动和调整的必要性。使这种调整进行得轻松些,也许是可取的,我们为此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例如实行失业保险等。但我们在努力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不应破坏制度的适应性。破坏制度的适应性,无异于杀鸡取蛋,自绝生财之道。不论我们做什么,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对国内外贸易一视同仁。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开展对外贸易有利可图?当前美国工人的生产率要高于日本工人的生产率。究竟高多少难以确定,每人的估计不一样。我们暂且假设高一半。那么平均说来,美国工人的工资可以买到的东西就应该是日本工人的一倍半。让美国工人来做任何事情,如果效率达不到日本工人的一倍半,就是浪费。用一百五十多年前创造的经济行话来说,这就是所谓相对有利条件原则。即使我们生产每种东西都比日本人更有效率,我们也不应样样都生产,这样做是不上算的。我们应当集中搞那些我们最内行的事,那些最能发挥我们优越性的事。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位律师会打字,比他的秘书快一倍,他就应当把这个秘书解雇而自己打字吗?如果这位律师打字比他的秘书强一倍,而干律师工作强五倍,那么他搞法律事务,让秘书去打字,他们的生活都会过得更好。
另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的根源据说是外国政府向它们的生产者提供补贴,使他们能够在美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假定一个外国政府提供这样的补贴(无疑,有些政府正是这样做的),受损失的是谁,得好处的又是谁,外国政府为了提供补贴,就得向公民征税。出钱补贴的是这些公民,得益的是美国消费者。他们得到便宜的电视机或汽车或是别的什么得到补贴的东西。我们应该抱怨这种反过来的外国援助计划吗,我们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或后来的援外计划把货物和劳务送给别国作为礼物是高尚的,难道外国以低于成本的价钱把货物和劳务卖给我们,以这种间接形式送礼就不光彩了吗?倒是外国公民应该抱怨。为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和本国受到补贴的工业的业主和工人的利益,他们必须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无疑,如果外国政府突如其来地或毫无一定规律地提供补贴,会给美国国内生产同样产品的工业的业主和工人造成不良影响。然而这是做生意通常要冒的危险。企业决不会抱怨使它发横财的不平常事件或意外事件。自由企业制度就是一个赢利和赔钱的制度。正如前面指出过的,任何用来缓和调整以适应突然变化的措施,都应该对国内和国外贸易一视同仁。
总之,混乱很可能是暂时的。假定由于某种原因,日本决定大量补贴钢铁工业。如果不增加关税或施行限额,输入美国的钢铁会急剧增加。这将使美国国内的钢铁价格下跌,迫使钢铁生产者减产,造成钢铁业的失业。另一个方面,钢铁制品的价格则可能下降。买这些产品的人将有多余的钱可用来买别的东西。对其他东西的需求会增加,生产这些东西的企业的就业人数也会增加。自然,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吸收现在失业的钢铁工人。但是其他工业里原来失业的工人将有工可作,能抵消这种影响。总的就业人数不一定会减少,而由于钢铁业不再需要的工人可以用来生产别的东西,生产将会增加。
这种由于片面地看问题而产生的谬见,同样表现在有些人为了增加就业而要求征收关税的行动上。譬如说对纺织品征收关税,国内纺织业的就业和产量会增加。但是,外国生产者不能在美国出售他们的纺织品,他们赚得的美元就会减少。赚得的美元减少,他们能花在美国的钱也就随之减少。因而进口减少多少,出口也会减少多少。纺织业的就业人数会增加,但出口工业的就业人数会减少。而工人转移到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去,会使总产量减少。
说国内钢铁业兴旺是国防所必需,这种国家安全论也没有更多根据。国防的需要只占用美国国内用钢量的一少部分。而且不可想象,钢铁的完全自由的贸易会毁掉美国的钢铁业。由于接近材料和燃料的来源,接近市场,只会有利于保障国内相对巨大的钢铁工业。的确,由于需要应付外国的竞争而不是受到政府的壁垒的掩护,很可能造就一个比我们现有的更为强大和有效的钢铁业。
【按:提高钢铁行业的反脆弱性,降低钢铁行业的垄断程度。】
假定那不可能发生的事果真发生了,假定确实到国外去买全部我们需用的钢更来得便宜。也还有其他办法确保国家安全。我们可以囤储钢铁。这很容易,因为钢铁占地方较少而且不会腐烂。我们可以封存一些钢厂,就象封存船只一样,需要时再启用。无疑还可以有别的办法。钢铁公司在新建一座钢厂以前,先研究几种不同的方案,以选择最优、最经济的厂址,然而钢铁业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提出那么些补贴的要求,却从未说明采用其他方法来保障国家安全要花费多少。除非他们能说明,我们可以肯定国家安全论是工业的自我利益的饰词,而不是补贴的正当理由。
无疑,钢铁业的经理们和钢铁工人工会人员提出国家安全的论据是真诚的。真诚这种德性被估价得太高了。我们都能够说服我们自己,相信对我们好的对国家也好。我们不应当埋怨钢铁生产者提出这种论点,而应怪我们自己相信了它。
说我们必须保卫美元,我们必须不让它同其他货币——日元、西德马克或瑞士法郎——的比价跌落,这个论点怎么样?这完全是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问题。如果外汇率是在自由市场上决定,它就会定在收盘时的比率。这样产生的美元对譬如说日元的比价,可能暂时跌到合理的水平以下,低于按美元算的美国货和按日元算的日本货的相对成本。要是这样,这就会给予注意到这个情况的人一种刺激去买进美元,留存一些时候,等其比价上升来获利。由于降低了出口到日本的美国货的日元价格,就会刺激美国出口;由于抬高了日本货的美元价格,就会减少从日本的进口。这些发展会增加对美元的需求而纠正开始时过低的比价。美元的价格,如果是自由确定的话,就同所有其他的价格一样,起同样的作用。它传递情报,提供促使根据情报采取行动的刺激,因为它影响进入市场的人的收入。
那为什么对美元的“疲软”生那么大气?为什么反复发生外汇危机?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外汇兑换率不是在自由市场上决定的。各国政府的中央银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来影响其货币的价格,在这一过程中,它们损失了它们公民们的巨额的钱(就美国来说,从1973年到1979年初,损失了将近二十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它们阻止了这一套重要的价格起其应有的作用。它们并没有能够阻止基本的经济因素对汇率最后产生影响,但却能够使人为的汇率维持很长时间。其后果是妨碍了适应基本因素的逐渐的调整。小的混乱累积成了大的混乱,最后发生一场严重的外汇“危机”。
为什么政府要干预外汇市场,因为汇率反映国内政策。美元比日元、西德马克和瑞士法郎弱,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比其他国家高得多。通货膨胀意味美元在国内能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少。它在国外能购买的东西也少了,这有什么奇怪呢,日本人、德国人或瑞士人不愿意按从前的比价兑换美元,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但政府也象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一样,总是费尽心机试图掩盖或抵消它们自己的政策造成的恶果。所以一个通货发得过多的政府就试图操纵汇率。当它失败的时候,就把国内通货膨胀归咎于汇率的下跌,而不承认正好相反的因果关系。
几世纪来,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各种论文书籍浩如烟海,主张征收关税的,只有三个论点在原则上还多少站得住脚。
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过的国家安全论。虽然这个论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征收某些特定关税的饰词而不是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有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确实需要维持一些不经济的生产设备。如果我们已不是在讨论理论上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在某种情况下确认为了加强国家安全有必要征收关税或对贸易实施其他限制,那就得比较一下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特定目标的代价,并确立至少表面上是确凿的证据,证明征收关税是代价最低的方法。但实际上却很少有人作这种比较。
第二个是“婴儿工业”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提出过这个论点。据说,有一种潜在的工业,一旦建立并在其痛苦的成长时期得到帮助,就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平等地进行竞争。据说,暂时征收关税是有道理的,是为了保护那处在襁褓中的潜在的工业,使它能长大成人,能自立地发展。即使那工业在建成后真正能成功地竞争,那也不能说明开始的时候征收关税是有道理的。就消费者来说,只是在一种情况下值得在开始时去补贴(他们用征收关税实际上做的事)那种工业,即他们往后通过某种方式,至少能收回补贴,例如使该工业产品的价格低于世界水平,或由于拥有这个工业而得到好处。但在这种情况下,补贴就是必需的吗,如果不提供补贴,最先进入那个工业的企业家开始时遭受的损失就真的得不到补偿了吗?归根结底,大多数公司在兴起时,头些年都要蚀本。它们进入一门新的工业是这样,进入一门已有的工业也是这样。也许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值得给予最初的投资,但最初的加入者遭受的损失却不能得到补偿。但推敲起来,其实并非如此。
婴儿工业论是一种烟幕。那所谓的婴儿老也长不大。一旦征收关税,就难再予以取消。而且,这个论点很少用来为真正还没有生下来的婴儿说话,这种婴儿要是能得到暂时的保护,本可以生下来并生存下去的。没有人为它们说话。这个论点用来主张征收关税,是为了那些颇上了些年纪的婴儿,他们已经能够施加政治压力了。
【按:需要关税保护的往往都是上了年纪的夕阳产业~。】
第三个不能立即排除的主张征收关税的论点是“以邻为壑”论。一个国家如果是一种产品的主要生产者,或者能够联合一些别的生产者一起控制大部分生产,可能利用它的卖主独家垄断地位抬高产品的价格(石油输出国组织就是当前的一个例子)。这个国家可以并不直接提价,而是间接地通过对产品征出口税——出口关税。它本身得到的好处可能抵不过其他国家的损失。但从本国的观点看,可以有所得。同样,一个国家如果是一种产品的主要购买者——用经济学行话来说就是拥有买主独家垄断力量——它可能通过同出售者讨价还价强使他们接受过低的价格,从中得到好处。一个办法就是对这种产品征收进口税。出售者净得的是减去了关税的价钱,这就是为什么征收进口税相当于以低价购买。事实上关税是外国人付的(我们想不出一个实在的例子)。实际上,这种民族主义的办法很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进行报复。此外,就婴儿工业论来说,实际的政治压力产生的关税结构,事实上既不利用卖主独家垄断地位,也不利用买主独家垄断地位。
第四个论点,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来而迄今被重复着的,是说自由贸易,要是所有其他国家都实行的话,会是件好事,但只要其他国家不实行自由贸易,美国也就无法实行自由贸易。这个论点,无论从原则上或在实践上都完全站不住脚。其他国家对国际贸易施加限制的确于我们有损,但那也损害它们自己。撇开上面谈过的三种情况不说,如果我们反过来也实施限制,我们只会给我们自己增加损失,也损害它们。竞相虐待绝不是处理敏感的国际经济政策的良方!这种报复行动不但不会使其他国家减少限制,相反,只会招致更多的限制。
我们是一个大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我们不应当要求香港、台湾规定纺织品的出口限额,以“保护”我们的纺织工业,而让美国的消费者和香港、台湾的中国工人吃亏。我们大谈自由贸易的好处,同时却运用政治经济力量使日本限制钢铁和电视机的出口。我们应当单方面走向自由贸易,不是一下子,而是经过一个时期,例如五年,按照事先宣布的速度进行。
很少有什么我们能够采取的措施,能比完全自由贸易更能促进国内和国外的和平事业。我们不应该以经济援助的名义赠款给外国政府,同时又对它们出产的东西施加限制,而应该采取一种一贯的和有原则的立场,因为赠款会促进社会主义,施加限制会妨碍自由企业的发展。我们可以告诉全世界:我们信仰自由并愿意实行。我们不能强迫你们实行自由。但我们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一切人提供充分的合作。我们的市场对你开放,没有关税或其他限制。你能够并愿意卖什么,就来这里卖好了,你能够并愿意买什么,就来这里买什么好了。这样,个人之间的合作就会成为世界范围的和自由的合作。
【按:“以经济援助的名义赠款给外国政府”往往是为了收买外国政府领导人特别是小致胜联盟的领导人。】
实行自由贸易的政治理由
相互依赖是当今世果上到处存在的特点;在经济领域本身,相互依赖存在于一套价格和另一套价格之间、一个工业和另一个工业之间、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之间。在更广泛的社会内,它存在于经济活动和文化、社会、慈善活动之间。在社会组织中,它存在于经济安排和政治安排之间、存在于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
在国际领域中也是一样,经济安排和政治安排交错在一起。国际自由贸易哺育不同文化和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正如国内自由贸易哺育不同信仰、态度和利益的个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一样。
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上,就如在任何国家的自由经济中一样,交易在私有的实体——个人、企业、慈善机构——之间进行。任何交易的条件,都由参加各方协议。除非各方都相信他们能从交易中得到好处,否则就做不成交易。结果,各个方面的利益取得了协调。普遍存在的是合作而不是冲突。
政府一插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一个国家里,企业从它们的政府那里谋求补贴,或者是直接的,或者以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的形式。它们将诉诸政治压力来使其他企业受到损失,规避威胁它们的利润以至生存的竞争者的经济压力。一国政府为了本国企业的利益进行干预,导致其他国家的企业向它们自己的政府寻求援助,来对抗外国政府采取的措施。私人之间的争议变成了政府之间的争议。每一次贸易谈判成了政治事件。政府高级官员乘坐喷气式飞机到世界各地去参加贸易会议。摩擦越来越大。各国人民对会议结果感到失望,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结果,普遍存在的是冲突而不是合作。
从滑铁卢到第一次世果大战的那一百年提供了一个显明的例子,说明自由贸易会对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多么良好的影响。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那一百年里,它实行了几乎完全自由的贸易政策。其他国家,尤其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各西方国家,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也许在形式上稍微有些不同。人们大体上都能按相互同意的条件,同任何人自由买卖,不管是住在哪里,住在同一个国家或不同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也许使我们在今天更感觉惊奇的是,人们可以自由地在整个欧洲旅行,或在世界大部分其他地方,不需要护照,也不受那重复的海关检查。他们可以自由移居,在世界大部分地方尤其是美国,可以自由入境并成为居民和公民。
结果,从滑铁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一百年,成了人类历史上西方国家之间最和平的时代。在这期间,只有过一些小战争,最著名的是克里米亚战争和普法战争。自然还有美国国内的大内战,它本身就是美国背离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而实行奴隶制的结果。
在现代世界上,关税和与此相类似的对贸易的其他限制,变成了国家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根源。但带来巨大麻烦的根源,却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当年的集体主义国家如希特勒的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佛朗哥的西班牙和现在的共产党国家如苏联及其卫星国和中国,都对经济进行干预。关税之类限制歪曲价格制度传递的信号,但至少还让个人有对这些信号作出反应的自由。集体主义的国家引入了影响深远的控制成分。
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公民同集体主义国家的公民之间,不可能进行完全的私人交易。有一方必定得由政府官员为代表。政治考虑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实行市场经济的政府容许其公民尽可能直接地同集体主义的政府作交易,摩擦可以减少。要想用贸易作为政治武器或用政治措施作为手段来增加同集体主义国家的贸易,那只会使不可避免的政治摩擦变得更厉害。
国际自由贸易和国内竞争
国内竞争的规模同国际贸易安排有密切关系。十九世纪后期,公众反对“托拉斯”和“垄断”的呼声导致建立了州际商业委员会并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这个法案后来受到许多其他立法行动的补充,来促进竞争。这些措施产生了很混杂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它们增加了竞争,但在另一些方面又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但是,即使这些措施完全达到其发起人的预想,也不能象取消国际贸易的一切限制那样,保证有效的竞争。在美国,虽然仅仅存在三大汽车生产者,而且其中之一已濒于破产,但这却对垄断价格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果让全世界的汽车生产者都来同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竞争美国的买主,那垄断价格的幽灵肯定会消失。
其他方面也是这样。没有政府以关税或其他办法公开和暗中的帮助,在一个国家里是很难确立垄断地位的。在世界范围,这更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德比尔公司对钻石的垄断,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看来成功的例子。我们不知道还有别的能没有政府的直接帮助而维持很久的垄断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早先的橡胶和咖啡卡特尔也许是受到政府帮助的最突出的例子。但是大多数这类由政府主持的卡特尔都维持不了多久。它们在国际的竞争压力下垮台了——我们相信石油输出国组织也会是这个下场。在一个实行自由贸易的世界上,国际卡特尔会更快消失。即使在贸易受到限制的世界上,美国也能够通过实行自由贸易(必要时单方面实行),来基本上消除国内的大垄断集团带来的威胁。
中央经济计划
在不发达国家旅行,我们一次又一次得到深刻的印象,那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所认为的事实同事实本身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异。
各地的知识分子都想当然地认为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是用来剥削人民大众的办法,而中央经济计划是未来的潮流,会把他们的国家推上迅速发展的道路。前不久,一位美国人批评印度的中央计划搞得过细,对此,一位很富有的而且文化修养极高的著名印度企业家——他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讽刺的那种大腹便便的资本家——进行了反驳。他明确告诉我们,象印度这样穷的国家的政府,只有控制进口、国内生产和收入的分配,也就是说,在所有这些使他发财致富的领域,授予他特权,才能保证社会的需要优先于个人的自私的需要。他只不过是重复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教授和知识分子的见解而已。
事实本身与这种见解大不相同。凡是个人自由的成分较大,普通公民的物质享受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增加,人们普遍对未来的发展抱有信心的地方,我们总是发现其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自由市场组织的。凡是国家严密控制其公民经济活动的地方,也就是说,凡是详细的中央经济计划统治一切的地方,那里的普通公民就受到政治的束缚,生活水平低下,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国家可能兴旺,可能开创不朽的功业,但普通公民成了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收入仅够维持他们适度的生产。
最明显的例子是东西德的对比。那本是一个整体,战争把它分成了两部分。居住在两边的人属于同一血统、同一文明,具有同样水平的技术和知识。哪一部分兴旺了,哪一部分不得不用墙来把它的公民关在里面,哪一部分今天必须用武装警卫并借助猛犬和地雷来对付那些勇敢而绝望的公民,他们宁愿冒生命的危险要离开他们的共产主义天堂,投向墙那边的资本主义地狱。
【按:这里都被删除了,哎!】
在墙的一边,街道灯火辉煌,商店里满是熙熙攘攘、兴高采烈的人群。一些人在购买来自全球的货物。另外一些人奔向众多的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他们可以自由地买到表达各种意见的报章杂志。他们可以互相或同陌生人交谈任何问题,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各种见解。走上几百步,排上一小时的队,填好表格,领到要交回的通行证,你就可以象我们那样去到墙的另一边。那里,街道是空荡荡的;城市灰色而苍白;商店的橱窗毫无生气;建筑物表面积满了污垢。三十多年了,战争的破坏还没有修复。在东柏林短暂的访问期间,我们发现,洋溢着欢乐气氛的唯一地方是娱乐中心。在东柏林呆上一小时就足以理解为什么当局要修建那堵墙了。
西德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从一个被打败和被摧残的国家变成欧洲大陆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是自由市场创造的奇迹。当时德国的经济部长是个经济学家,名叫路德维希·艾哈德。1948年6月20日是星期天。在这一天,他下令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就是今天的西德马克,同时取消了差不多所有对工资和物价的管制。正如他常说的那样,他之所以在星期天采取行动,是因为法、美、英占领军当局星期天不办公。他深信,要是在其他日子采取行动,那些对管制抱赞同态度的占领军当局准会取消他的命令。他的措施象是具有魔力。几天之内,商店里便摆满了货物。几个月之内,德国的经济就活跃起来了。
即便是两个共产党国家苏联和南斯拉夫,也形成了类似的对比,虽然不那么极端。苏联是严格地由中央控制的。它没有完全取消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但它尽可能地限制它们的范围。开始时,南斯拉夫走同样的道路,但在铁托同斯大林的俄国破裂之后,它急剧地改变了它的路线。它仍是共产主义的,但谨慎地实行分散化并运用市场力量。大部分农田归私人所有,其产品可以在比较自由的市场上出售。私人可以经营雇工不超过五人的小企业。小企业,特别是手工业和旅游业方面的小企业获得了很大发展。大企业是工人合作社——一种效率不高的组织形式,但至少使个人能在一定程度上肩负责任并发挥主动精神。南斯拉夫的居民是不自由的。他们的生活水平比邻国奥地利或其他西方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低得多。然而,南斯拉夫还是给从俄国去的有观察力的旅游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较之下它是天堂。
在中东,尽管以色列宣布的是社会主义的哲学和政策,并且政府广泛地干预经济,但它仍然具有强有力的市场因素,这主要是对外贸易在以色列的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产生的间接后果。它的社会主义政策妨碍了它的经济成长,但是它的公民比起埃及的来,享有更多的政治自由和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埃及的政治权力更比以色列集中得多,其经济活动受到的控制也要比以色列严格得多。
在远东,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和日本,都广泛地依赖私人市场,因而都很兴旺发达。它们的人民充满希望,经济正在迅猛发展。最好的衡量标准是,七十年代后期,这些国家平均每人的年收入,最低的约达七百美元(马来西亚),最高的约达五千美元(日本)。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共产党中国都严重依靠中央计划,因而都经历了经济停滞和政治压制。这些国家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不到二百五十美元。
主张中央经济计划的知识界人士曾经为毛的中国高唱赞歌,可没想到毛的继承人则大讲中国的落后并埋怨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没有取得进步。他们所设想的促进现代化的措施之一,就是让物价和市场起比较大的作用。同在南斯拉夫一样,这种策略将使中国当前低下的经济水平大大提高。但是,只要对经济活动仍保持严格的政治控制,私有财产仍受严密限制,这种提高就将大大受到限制。而且,即使是在这样有限程度上放出个人积极性的妖怪来,也会引起政治问题,迟早大概会产生反应,导致更大的独裁。另一种结果,共产主义垮台,被市场制度所取代,看来远不那么可能,虽然作为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并不完全加以排除。同样,一旦年迈的铁托元帅去世,南斯拉夫将经历政治上的不稳定,可能产生反应,导致更大的独裁,或者远不那么可能的,导致现存集体主义的安排的破产。
【按:这里都被删除了,哎!】
值得更详细地考察的一个特别显明的例子,是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对比——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最初三十年的经历,和日本在1867年明治维新后最初三十年的经历。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般说来很难象物理学家那样作有控制的实验,这种实验在验证假设上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在这里,经验产生的一些东西,很接近于有控制的实验,我们能够用以检验经济组织方法上的差别的重要性。
中间相隔八十年。但在所有其他方面,在我们拿来比较的开始时期,两国的情形很相象。两者都有古老的文明和发达的文化。两者都有高度结构化的人口。日本是封建结构,有大名(即领主)和农奴。印度是严格的等级制,按照英国人“排定的等级”,最上面是婆罗门,最底下是贱民。
两个国家都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革,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安排方面发生剧烈的变动。在两国内,都有能干的、虔诚的领袖掌权。他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决心使经济的停滞变成迅速的增长,把他们的国家转变成大国。
几乎所有的差别都对印度,而不是对日本有利。日本先前的统治几乎使它同其余世界完全隔绝,国际贸易和接触限于一年一次的荷兰船只的访问。少数被准许呆在那个国家的西方人,被圈在大阪港口一个小岛上的居留地内。三个多世纪的强行隔绝,使日本对外部世界茫无所知,在科学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除中文外,几乎没有人能够讲或者读外语。
印度要幸运得多。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得到巨大增长。这种增长,在两次大战之间因从英国争取独立的斗争变成停滞,但并没有倒退。运输的改进结束了过去反复发生的地区性饥荒。它的许多领袖曾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受教育,尤其是在英国。英国的统治留下了一批高度熟练和有训练的民政人员、现代的工厂和一个非常完好的铁路系统。这些在1867年的日本一样也没有。印度在技术上虽比西方落后,但差距小于1867年的日本同当时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
印度的物质资源也比日本优越得多。日本在物质资源上的唯一优势大概是海洋,使得交通方便并提供大量的鱼。日本只有此一项优势,其他全不如印度。印度的幅员约为日本的九倍,而且有大得多的面积是比较平坦和交通便利的土地。日本则大部分是山区,它只沿着海岸有一条狭长的可居住和可耕种的地带。
最后,日本没有得到半点外援。在日本没有外国投资,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或基金会赠款给日本或提供低利贷款。它不得不依靠自己筹措资金来发展经济。它也曾有过一次幸运的例外。在明治维新后的早期,欧洲的蚕茧严重歉收,这使得日本能够靠出口生丝赚得比平时要多的外汇。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偶然的或有组织的重要的资金来源。
印度的境况要好得多。自从1947年独立以后它从世界上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大部分是赠送的。这种输送现在也还在继续着。
尽管1867年的日本和1947年的印度情况相似,其结果却大不相同。日本摆脱了封建结构,让所有的公民都有社会和经济的机会。普通老百姓的境况迅速改善,虽然人口陡然增长。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本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虽然它没有实现完全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但在这方面却取得了巨大进展。
印度口头上废除等级限制,但实际上很少进展。少数人和多数人在收入和福利方面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象八十年前的日本一样,印度的人口猛增,但按人口平均的产量却没有按同样的速度增长。其经济仍然近乎停滞。那最贫穷的三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英国统治结束后,印度曾夸耀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没过多久,就开始实行独裁统治,限制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目前,它正处于重新这样做的危险之中。
怎样解释这两种结果的差别,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人的性格所造成的。据说,宗教戒律、等级制度、宿命哲学——所有这些把印度人民禁锢在传统的束缚之下。据说印度人缺少进取心而且懒惰。而日本人则受到称赞,说他们有干劲、精力旺盛、热心于接受外来的影响,而且难以置信地善于把从外边学到的东西加以改造利用。
关于日本人的这种描绘在今日可能是对的。但在1867年却不是这样。当时居住在日本的一个外国人写道:“我们不认为它(日本)会变得富有。自然赋予的长处,除了气候,以及人民自己的爱好懒惰嬉戏,妨碍了它。日本人是一个愉快的种族,有一点就满足,不大可能取得很大成就。”另一个写道:“在世界的这部分,西方确立和公认的原则,好象失去了它们原先具有的效力和活力,并致命地倾向于芜杂和腐败。”
同样,关于印度人的描绘也可能符合今天印度国内的一些印度人,甚至可能符合大多数,但它肯定不符合侨居别处的印度人。在许多非洲国家,在马来西亚、香港、斐济群岛,巴拿马以及新近在英国,印度人是成功的企业家,有时候还成了企业界的台柱子。他们常常是发动和推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印度国内,只要是能避开政府控制的铁手的地方,事业心、积极性和干劲都有所表现。
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不取决于群众的品行。在每一个国家,一小部分人确定步子,决定事件的进程。在发展得最快最成功的国家里,一小部分事业心强、甘冒风险的人闯在前面。为仿效者创造跟随的机会,使大多数人得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率。
许多外界观察者探讨的这种印度人的特征,与其说是缺少进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其反映。当卖力干和冒风险得不到报酬的时候,懒惰和消沉就会滋生。宿命的哲学是同停滞相适应的。印度并不缺乏人材,能发动和推进经济发展,就象日本在1867年所经历,或者甚至象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经历的那样。的确,印度的真正悲剧是,它本可以——我们相信——成为一个繁荣昌盛而生气勃勃的自由社会,但目前却仍然是一个满是穷困潦倒的人民的次大陆。
我们新近碰到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经济制度如何能够影响人的性格。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流入香港的中国难民,推动了它的经济飞快发展,并以他们的积极性、事业心、勤俭和干劲得到了应有的尊敬。中国新近放宽对移民的限制之后,产生了一批新的侨民——来自同一种族,具有同一基本的文化传统,但经过三十年共产党统治的抚育和塑造。我们听到一些雇用这些难民的公司说,他们与早先来香港的中国人大不相同。新来的移民非常缺少主动性,需要人家确切告诉他做什么。他们懒惰,不合作。无疑,在香港的自由市场呆上几年之后,他们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的。
那么,对于1867年至1897年的日本和1947年到现在的印度之间的不同经验该作何解释呢?我们相信,其解释同东西德之间、以色列和埃及之间以及台湾和红色中国之间的差别一样。日本按照当时英国的模式,主要依靠自愿的合作和自由市场。印度则按照当时英国的模式,依靠中央经济计划。
明治政府也曾多方面进行过干预,在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它送许多日本人出国接受技术训练,邀请了许多外国专家。它在许多工业中建立了领头的工厂,并给与其他工业许多补助。但是没有哪个时候它曾经试图控制投资的总额或方向或是生产的结构。国家只在造船业和钢铁业保持大量的股权,因为它认为这是军事力量所必需的。它维持这些工业,因为它们对私人企业没有吸引力,需要大量的政府补助。这些补助消耗日本的资源。它们妨碍而不是刺激日本经济的进展。最后,一项国际条约禁止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头三十年征收高于5%的关税。这种限制证明对日本完全是一件好事,虽然当时曾遭到埋怨,而且在条约的限制期满后就提高了关税。
印度执行了一条与此大不相同的政策。它的领袖们把资本主义看作帝国主义的同义语,不惜任何代价要加以避免。他们制订了一系列俄国式的五年计划,详细地规定了投资项目。某些领域的生产为政府所保留;私人公司容许在其他领域经营,但必须同计划一致。关税和限额控制了进口,补贴控制了出口。自给自足是理想,不用说,这些措施造成外汇短缺。这又用严密而广泛的外汇管制来对付,外汇管制成了无效率和特权的一大根源。工资和物价受到管制。要盖个工厂和进行其他投资必须得到政府批准。无处不有的税,纸面上定得很高,实际上大量逃漏。各种各样的走私、黑市和非法交易,就象赋税一样无处不有,破坏了法制的威信,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中央计划的死板,使得有可能满足紧急的需要,从而起了有价值的社会作用。
在日本,依靠市场,挖掘了潜在的、意想不到的能力和才干的资源。它阻止了妨碍改革的既得利益。它强使发展接受效率的严峻考验。在印度,依靠政府的控制,挫伤了积极性或将它付诸东流。它保护了既得利益不予改革。它用官僚主义的批准代替市场的效能,作为生存的尺度。
这两个国家的家庭纺织品和工厂纺织品的经历可以说明政策上的区别。1867年的日本和1947年的印度,家庭纺织业的规模都很大。在日本,外国的竞争没有对家庭生产的生丝产生多大影响,这也许是因为日本的生丝优越,加上欧洲的歉收;但它几乎完全排挤了土制棉纱,后来又排挤了土布。日本的纺织业工厂发展起来了。开始它只制造最粗糙的、最低档的纺织品。后来制造越来越高级的纺织品,最后成了一门大出口工业。
在印度,手工纺织得到补助并保证有其市场,据说是为了缓和向工厂生产的过渡。工厂生产逐渐增加,但为了保护手工纺织业,被有意地加以限制。保护意味着扩大。手工织机从1948到1978年大约增加了一倍。今天,在全印度成千上万的村庄里,从早到晚可以听到手工织机的声音。如果是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其他工业竞争,有一门手工纺织业并不坏。在日本,现在还存在一门虽然极小但是兴旺的手工纺织业。它织造高级的丝绸和其他织品。在印度,手工纺织业的发达是因为得到政府的补助。实际上,政府向那些生活并不比手工织机工人好的人征了税,以使手工织机工人的收入高于他们从自由市场上赚得的收入。
十九世纪初期英国面临的问题,同几十年后日本所面临的和一个多世纪后印度所面临的问题正好一样。动力织机有摧毁兴旺的手工纺织业的危险。英国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这门工业。它显然考虑了印度采取的那种政策:补助手工纺织业,保证它的市场。但该委员会立即否定了这项政策,理由是这只会使根本的问题——手工织工过多,变得更严重。这正是印度所发生的情况。英国采取了同日本一样的解决办法——暂时是严酷的,但最后是慈善的政策,让市场力量起作用。
印度和日本的这种对比很有趣,因为它不仅如此清楚地表明两种组织方法的不同结果,而且表明在追求的目标和采取的政策之间并无关系。明治维新统治者——他们立志要加强他们国家的权力和荣誉而很不重视个人自由——的目标同印度的政策更合拍,而不是同他们自己采取的政策。印度的新领袖们——他们热衷于个人自由——的目标同日本人的政策更合拍,而不是同他们自己采取的政策。
控制和自由
美国虽然没有实施中央经济计划,但在过去五十年里,我们在经济中扩大政府的作用已经够多了。这种干预使我们在经济上付出了很大代价。对经济自由施加的限制,使我国两个世纪来的经济发展有归于结束的危险。干预也使我们在政治上付出了很大代价。它大大地限制了我们的个人自由。
美国主要还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世界上最自由的大国之一。但是,正如林肯在那有名的“分裂的家”的演说中所说:“一个家分裂开来反对自己,就不能维持。……我不期望这个家会垮掉,我确实期望它不再分裂。它要么完全归一,要么完全变样。”他是在讲对人的奴役。他的预言同样适用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要是在这方面走得太远,我们分裂的家会倒向集体主义一边。幸运的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公众正在认识到这个危险,决心阻止并扭转政府干预越来越多的趋势。
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现状的影响。我们倾向于这种看法:当前的局面是理所当然的,是事情的正常状态,特别是当事情是由一系列小的和渐进的改变来形成的时候更是如此。要估计那累积起来的影响有多大是困难的。需要发挥想象力,超脱现状,用新的眼光来加以观察。这是很值得做的事情。结果要不是令人吃惊的话,大概也是会出人意外的。
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自由选择如何使用我们的收入:多少用在我们自 己身上,花在什么项目上;多少存起来,用什么方式;多少给别人,给谁。现在,我们收入的40%以上是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代表我们花掉的。有人曾提出规定一个新的国庆日,叫个人独立日——在每年的这一天,我们不再为政府的开支而工作……而是为了支付几个人或单独一个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愿望选定的项目而工作。”在1929年,这个节日也许应该定在2月12日,林肯的生日这一天;今天,也许应该定在5月30日;如果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到1988年左右它会碰上另一个独立日,7月4日。
自然,我们对政府代表我们花多少我们的收入,有一些发言权。我们参与了那个政治过程,这个过程使政府花费了我们 40% 以上的收入。多数通过的办法是一种必要和可取的权宜之计。但是这同你在超级市场上买东西时的那种自由很不一样。当你一年一度去投票的时候,几乎总是投一揽子的票而不是投特定项目的票。如果你是多数,最好的情况是,你在得到你所愿意要的项目的同时也将得到那些你反对的项目,只是比较起来不认为那么重要罢了。通常的结果是,你得到的东西并不是你当初投票赞成的东西。如果你是少数,你就必须服从多数的表决,等待下一次机会。当你每天在超级市场上投票时,你得到的就是你投票要的东西,别的人也是一样。投票箱产生的是遵守而并不一致,市场产生的是一致而无遵守。这就是为什么要尽可能把表决方法只用于那些必须遵守的决定的原因。
【按:新版翻译是“投票箱产生的结果是被迫一致而非自愿一致,而市场产生的结果则是自愿一致而非被迫一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仅在需要被迫一致才能做出决策的时候才选择投票箱这种办法,而且能不用就不用。”】
作为消费者,我们甚至不能自由选择怎样使用纳税后剩下的那部分收入。我们现在不能自由购买甜味素,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连糖精也不能随意购买了。我们的医生不能自由地为我们开许多药,尽管他认为这些药对我们最有效,或者这些药在国外已经广为使用了。我们不能自由地购买一辆没有座位安全带的汽车,虽然眼前我们仍可以自由选择是系它还是不系它。
经济自由的另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按照我们自己对价值的看法自由地使用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自由从事任何职业,加入任何企业,同任何别人作买卖,只要是在严格自愿的基础上这样做,不诉诸强力来强制别人。
今天,你不能自由地作为一个律师、内科医生、牙科医生、管子工、理发师、殡仪人提供你的服务,或是从事其他许多职业,除非先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批准或证书。你不能自由地按照你同你的雇主协商好的条件加班,除非条件符合政府官员定下的规章。
你不能自由地设立银行、进入出租汽车行业或从事出售电力或电话服务的企业或经营铁路、公路或航线,除非先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
你不能自由地在资本市场筹集资金,除非你填好证券交易委员会需要的多种表格,而且能使证券交易委员会满意于你提出的计划书。该计划书必须把前景描绘得如此暗淡,以至没有哪一个头脑清醒的投资者会愿意对你的计划投资,才会使证券交易委员会满意。而且,要取得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批准,可能得花费十万多美元——这肯定会吓退我们的政府声称要资助的小企业。
拥有财产的自由是经济自由又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们的确广泛地拥有财产。我们当中的多数人拥有所住的房子。但是谈到机器、工厂和类似的生产手段,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们自称是一个私人企业的自由社会,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但就公司企业的所有权来说,我们大概46%是社会主义的。拥有1%的股份意味着你有权分到1%的利润,并必须用你全部资产的价值分担1%的损失。1979年联邦的公司所得税率是十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必须缴纳46%的所得税(1979年以前为48%)。联邦政府从每一美元的利润可得四十六美分,它也分担每一美元损失的四十六美分(如果有早先的利润可以抵消这种损失的话)。联邦政府拥有每一公司的46%——虽然不是以直接参预决定公司事务的形式。
甚至仅是列举出加于我们经济自由的全部限制,也得一本比此书更厚的书,更不用说来详细描述了。上述例子只是用来说明,这种限制已变得多么普遍。
人类自由
对经济自由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影响一般的自由,以至言论出版自由也受到了影响。
让我们看一看下面这些从李·格雷斯1977年的一封信中摘出来的话,他是那时一个石油 煤气协会的执行副会长。关于能源立法问题,他写道:
如你们所知道的,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一千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应该定多高价格的问题,而是宪法第一号修正案的延续,即保障言论自由的问题。随着限制的增加,就像老大哥越来越紧地盯着我们,我们胆怯起来了,不敢说出真相,不敢揭露谎言和错误。我们对国内收入署的查帐、官僚主义的扼杀或政府的刁难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心理是反对言论自由的一项强大的武器。
10月31日(1977)出版的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华盛顿小广播”栏里指出:“石油业的职员们声称,我们接到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的最后通碟:‘支持政府提出的原油税——不然就要面临更严格的规定和可能发动的一场运动来拆散石油公司’。”
他的判断为石油业人员的公开行为所充分证实。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斥责他们赚取“污秽的利润”,一批石油业的经理中间竟没有一个人顶他,或是退出会议室,拒绝再受人身攻击。石油公司的经理们私下对现行限制他们活动的复杂的联邦控制结构或卡特总统提出的大大扩大政府干预的办法,表示强烈的反对,但却发表措辞温和的公开声明,赞成控制的目标。
几乎没有企业家认为卡特总统的所谓自愿的工资物价管制是对付通货膨胀的可取的或有效的办法。然而,他们却争先恐后地颂扬那个计划,并答应予以合作。只有少数人,如前国会议员、白宫官员和内阁成员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有勇气公开加以谴责。另一个敢于讲的人是那个八十高龄的执拗的前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
为了言论自由,人们完全应当付出代价——如果只是不吃香、挨批评的话,也许还能忍受。但这代价应当是合理的而不是过分的。决不应该如有名的最高法院裁决所说的对自由言论产生“令人胆寒的影响”。然而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是,当前对企业的经理们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影响。
这“令人胆寒的影响”并不只限于在企业经理们身上。它影响我们全体。我们最熟悉学术界。我们的同行中间,有许多人,搞经济学的和自然科学的得到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补助;搞人文的得到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补助;所有在大学教书的教师都从州的立法机关那里得到他们的一部分薪金。我们认为,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对高等教育的税款补助都是不可取的,应当予以取消。这无疑在学术界还是一个少数人的意见,但这个少数人比人们从公开声明中所能搜集到的要多得多。
新闻界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政府——不仅作为主要的新闻来源是这样,而且在许多日常事务中也是这样。看一看英国的一个惊人的例子。伦敦《泰晤士报》这样一份大报,几年前有一天被它的一个工会阻止不能出版,原因是该报打算发表一篇报道,讲工会企图影响报纸的内容。结果,劳资纠纷使这家报馆完全关闭,有关的工会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得到政府的特别的庇护。英国一个全国性的记者联合会正在发起成立记者组织,并威胁要抵制那些雇用不属于他们这个联合会的人员的报纸。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个堪称为自由发祥地的国家里。
就宗教自由来说,在美国,阿密希的农民的房屋财产曾被没收,因为他们以宗教的理由拒绝交纳社会保险税——也不接受社会保险。教会学校的学生曾被作为逃学者、违反强制上学法被传讯,因为他们的教师没有那必要的纸片,证明他们满足了州政府的要求。
【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只是一句口号。。】
虽然这些例子只是反映了些表面的现象,它们却说明了基本的道理:自由是个整体,任何事情如果减少我们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自由,它也就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自由。
自由不可能是绝对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社会中,对我们的自由施加某些限制是必要的,以免遭受其他更坏的限制。但是,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一点,当今迫切需要的是取消限制而不是增加限制。
本节内容概述
自由贸易不仅能促进我们的物质福利,而且还能促进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协调,鼓励国内的竞争。
主张征收关税的,只有三个论点在原则上还多少站得住脚。
第一个就是国家安全论。
第二个是“幼稚产业”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提出过这个论点。
第三个不能立即排除的主张征收关税的论点是“以邻为壑”论。
互加关税----这种报复行动不但不会使其他国家减少限制,相反,只会招致更多的限 制。
我们可以告诉全世界:我们信仰自由并愿意实行。我们不能强迫你们实行自由。但我们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一切人提供充分的合作。我们的市场对你开放,没有关税或其他限制。你能够并愿意卖什么,就来这里卖好了,你能够并愿意买什么,就来这里买什么好了。这样,个人之间的合作就会成为世界范围的和自由的合作。
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上,就如在任何国家的自由经济中一样,交易在私有的实体——个人、企业、慈善机构——之间进行。任何交易的条件,都由参加各方协议。除非各方都相信他们能从交易中得到好处,否则就做不成交易。结果,各个方面的利益取得了协调。普遍存在的是合作而不是冲突。
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公民同集体主义国家的公民之间,不可能进行完全的私人交易。有一方必定得由政府官员为代表。政治考虑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实行市场经济的政府容许其公民尽可能直接地同集体主义的政府作交易,摩擦可以减少。要想用贸易作为政治武器或用政治措施作为手段来增加同集体主义国家的贸易,那只会使不可避免的政治摩擦变得更厉害。
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不取决于群众的品行。在每一个国家,一小部分人确定步子,决定事件的进程。在发展得最快最成功的国家里,一小部分事业心强、甘冒风险的人闯在前面。为仿效者创造跟随的机会,使大多数人得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率。
不施加关税对相关产业的冲击----暂时是严酷的,但最后是慈善的政策,让市场力量起作用。
经济自由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自由选择如何使用我们的收入;经济自由的另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按照我们自己对价值的看法自由地使用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自由从事任何职业,加入任何企业,同任何别人作买卖,只要是在严格自愿的基础上这样做,不诉诸强力来强制别人。
自由不可能是绝对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社会中,对我们的自由施加某些限制 是必要的,以免遭受其他更坏的限制。但是,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一点,当今迫切需要的 是取消限制而不是增加限制。
附录英国“自由贸易”的真相
只能说当时英国的经济自由度显然高于其他国家,但英国本身离自由贸易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可以说当时各国的关税税率显著低于当前关税税率,不能说当时美国之类的实行的也是自由贸易。
如下片段来自英国历史学者约翰·霍布森的代表作《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11出版)一书: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1846 年并不标志着英国向自由贸易的转变。1846 年至 1860 年之间,英国关税保持在 20% 的高额水平,1860 至 1879年间仍保持在高达 10% 的水平。只在 1880 至 1913 年期间才降到适度的 6%。 …… 总之,关于英国工业化是基于放任主义的传统描述,虽然广为人知,但只是一种神话。英国的税收、关税、预算、赤字、国债和军事支出等因其数额之高而引人注目。
附录自由贸易的起源——儒学
详见第一章附录。
儒学强调「通商惠工」、「关市讥而不征」、「民富国富」,显然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
【李竞恒】《“关市讥而不征”: 原始儒家为何反对征收关卡税》
在张家山汉简《算数书》中,记载了战国末或汉初的关卡收税算术题,说商人带着盾、狐、狸、犬出关,要缴纳租税“百一十一钱”,百姓如果背着米出关,要经过三个关卡,“三税之一”,即三分之一的份额都要被榨取。
孟子认为,只要能更好地保护民间商业,废除沉重的关卡税,就会“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者皆欲出于王之涂”。
孟子主张自由贸易。在《孟子·梁惠王下》提出治国需要“关市讥而不征”,在《尽心下》中,他提出“古者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意思是古代建立关隘,是为了保护社会,而不是为了多收税,他主张对民间商业不收关隘税。这一点与英国《大宪章》第13条,免除各市、区、镇、港的关卡税,皆享有免费通关权的主张是一致的。
在商贸道路上设立关卡,孟子认为其功能是稽查犯罪即可,而不是用来收税,增加贸易负担。从考古资料来看,当时关卡商业税的负担不小。如包山楚简《集箸》简149记载了十个邑、四条水道日常都要收取“关金”,可见当时官府不但在陆地上收取关卡税,在水路上一样要榨取一笔。
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楚王颁发给鄂君启的车节和舟节,都有错金铭文,车节铭文云“得金节即毋征”,“不得其节即征”,意思是鄂君启这种特权者拿着楚王颁发的“金节”这一凭证,在通过关卡时就能享有不征税的特权,舟节铭文云:“见其金节毋征,毋舍桴饲;不见其金节则征。如载马、牛,差以出内关,则征于大府,毋征于关。”意思也是水路关卡上,凭借特权金节可以免除征税,但如果运载牛、马出关则由大府征税。显然,鄂君启这种特权者是极少数,绝大部分的普通商旅、百姓无论是走陆路还是走水路,经过各国关卡都是要遭受盘剥的。所谓“平民百姓不似鄂君启之权贵,通商行旅是要遭到重重关卡征敛的”。
在张家山汉简《算数书》中,记载了战国末或汉初的关卡收税算术题,说商人带着盾、狐、狸、犬出关,要缴纳租税“百一十一钱”,百姓如果背着米出关,要经过三个关卡,“三税之一”,即三分之一的份额都要被榨取,可见是民众和商旅的沉重负担。而特权者却并不缴纳通关税,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对于沉重的关卡之税,战国时期的思想中有批评的声音。如上博楚简《容成氏》是一篇带有儒家思想倾向的出土文献,其中就专门讲到了美好的大禹时代“关市无税”,不征收关卡税,而到了夏朝末年的桀王则相反,“以征关市,民乃宜怨”(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
孟子生活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自然会对沉重的关卡税提出批评。孟子的主张就是,各个关卡,无论贵族还是普通商人,都统统不收税,藏富于民,保护自由贸易。所以梁启超先生对这一主张的评价是:“儒家言生计,不采干涉主义”(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0页),可谓一语中的。孟子认为,只要能更好地保护民间商业,废除沉重的关卡税,就会“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者皆欲出于王之涂”(《孟子·梁惠王上》),天下的百姓、商人都希望来这个低税率和保护自由贸易的国家,行走在畅通无阻的陆路和水道上,市场则会进一步繁荣,国家经济发展了,其实长远对国家才有好处。
《孟子·公孙丑上》记载了孟子的商业思想:“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对于“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有不同说法。
笔者认为,对这一段解释比较合理的就是朱熹引用张载的注释“赋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货;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赋其廛”,“廛”是市场中的商业用地(邬勖:《秦汉商业用地制度初探:以出土文献为中心》),意思就是对市场商业用地只征收一点商业用地税就行了,不用征收货物税,此外要用市场法律提供守夜人最低秩序,而不再征收其它多的税赋。这种低税收和良好公共服务的状态,能吸引到各国的人都前来参与市场活动,促进经济的繁荣。
奥地利学派谈到,远古以来的人无法理解商业活动的实质。他们看到商业“贱买贵卖”,因此将其视为一种可怕的魔法。西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对商人表示藐视。西方的两希传统中都镌刻着蔑视商业活动的基因: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嘲讽商人是“是些身体最弱不能干其他工作的人干的”,耶稣则把商贩驱逐出圣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孔子、孟子那里从来没有对商人或商业行为的讥讽,相反,孔子经常熟练使用商业术语,原始儒学的贤人中更是出了儒商子贡,而到了孟子这里仍然强烈地为自由贸易进行辩护,这种对市场的态度,是原始儒学的重要属性之一。
附录联邦德国战后崛起之路
路德维希·威廉·艾哈德(德语:Ludwig Wilhelm Erhard,1897年2月4日—1977年5月5日),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被誉为“社会市场经济之父”。他从1949年到1963年被任命为联邦德国(西德)经济劳动部长,从1963年到1966年担任联邦德国(西德)总理。
从1945年到1946年,艾哈德在巴伐利亚州任商业和企业部部长,但这段时间里他的工作的成绩不大。
1947年,他领导英美占领区管理部门的特殊货币和贷款专家委员会研究货币改革。
1948年3月2日,德国自由民主党提名艾哈德为美英法联合占领区所组成的联合经济区的经济管理部门首长,这样艾哈德实际上就成为西部占领区的经济政策负责人。在西德进行货币改革前五天(1948年6月20日),占领国代表才通知他这项措施的实行。6月19日,艾哈德通过电台宣布取消价格约束和义务提供服务的规定。第二天美国占领军司令愤怒地将艾哈德招来训斥他自主改变了占领军的命令。艾哈德回答说:“我没有改变这些命令,我废除了这些命令。”今天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艾哈德的这个自主行动是后来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主要条件。
艾哈德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奠基人之一,他召集了威廉·勒普克等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为经济部副部长,他们对德国开始时期的经济政策的影响非常大。艾哈德本人始终反对将当时德国经济的发展称为“经济奇迹”,他本人总是说,世界上没有奇迹。他认为这个发展是成功的市场经济政策的结果。
附录柏林墙
柏林围墙又称柏林墙(德语:Berliner Mauer)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期间,隶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政府环绕西柏林边境修筑的全封闭边防系统。它最早建于1961年8月13日,全长167.8公里,最初以铁丝网和砖石为材料,后期加固为由瞭望塔、混凝土墙、开放地带以及反车辆壕沟组成的边防设施。东德政府称此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德语:Antifaschistischer Schutzwall)和“强化边境”(德语:Befestigte Staatsgrenze),建造柏林墙的目的在于阻止东德居民通过西柏林前往西德。因为柏林墙把西柏林地区如孤岛一般地包围封锁在东德范围之内,所以也被称之为“自由世界的橱窗”(德语:Schaufenster der freien Welt)。它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更是分割东西欧的铁幕的象征。
柏林墙的建立是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之间冲突导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纳粹德国首都柏林被分割为东柏林与西柏林;在柏林墙修建之前,共计约有350万东德居民逃离苏占领区以及之后的东德,其中1949年到1961年逃离的人数约为260万。此外还有大量波兰人与捷克斯洛伐克人将柏林视为其通往西方的通道。许多人通过西柏林前往西德和其他西欧国家。柏林墙修建后在1961至1989年间这类逃亡被大幅限制下来,约有5,000人在此期间尝试翻越柏林墙。1962年起《开枪射击令》生效,东德边防军允许对非法越境者开枪射击,此举于1982年甚至通过立法被合法化。据截止2009年的统计,被枪杀人数约在136人至245人之间,确切死亡人数目则不得而知。
1989年东欧国家发生了一系列政治变革,邻国波兰和匈牙利政府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在数周的抗议活动后,1989年11月9日东德政府宣布允许公民申请访问西德和西柏林,当晚柏林墙在东德居民的压力下被迫开放。随后数周中欣喜的人群凿下柏林墙作为纪念品,1990年6月东德政府正式决定拆除柏林墙。柏林墙的倒塌为结束东德共产党的统治、东德政府的倒台以及两德统一奠定了基础;1990年10月3日,两德正式统一,而柏林亦成为两德统一后的新首都。
柏林墙建立后,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其中死亡人数存在一定争议。查理检查站博物馆负责人希尔德布兰特称死亡人数多于200人,波茨坦的当代历史研究中心(ZZF)已确认136人死亡,先前的官方统计为96人。
东德政府向边防守卫下达了《开枪射击令》,虽然随后东德官员否认这一命令的存在。研究者发现在一封1973年10月的命令中,守卫被告知尝试穿越围墙的人为罪犯,并且需要开枪射击:“使用你的武器时不要犹豫,即使违反边境禁令的是一队妇女和儿童,这是叛徒们常用的策略。”
早期围墙尚未修建时,东德的人们通常通过跳过铁丝网和从公寓窗口跳下来穿过边境,然而在柏林围墙修建后这种方式几乎绝迹。东德当局不允许靠近边界的公寓继续正常使用,并且用砖封住了边境附近建筑物的所有窗口。在得知柏林围墙修建消息的第三天,19岁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防军士兵康拉德·舒曼便跳跃过了当时低矮的铁丝网边境,进入西柏林。这一瞬间被西方媒体记者抓拍到,此事也成为了冷战期间西方用来广为宣传的样本。他也是第一个越境的边境守卫。艾达·西格曼为第一个因穿越围墙而丧生的人,她在1961年8月22日从柏尔诺街48号的三层公寓跳下后身亡。1961年8月当柏林墙建立起来之后,东德边防军就得到了开枪射杀所有尝试越境者的命令。1962年8月17日彼得·费希特尔试图翻越围墙逃往西柏林,在攀至顶部后被东德边防警察发现并开枪射杀。当时,东西两边的人民都看到他中枪,并有西方记者在场。西柏林边防军曾投掷急救包,并甚至有警察翻身跃墙将这位东德青年抬起来企图抢救,但东面却没有人施予援手,事件在冷战时期轰动一时,他成为了第一个因试图攀越柏林墙而被射杀的人。最后一个被射杀的人是1989年2月6日尝试越境的克里斯·格弗罗伊。
1997年3月,两名开枪的东德边防军士兵罗夫·费特列治和埃里克·薛伯分别被判刑20和21个月。
除直接翻越外,人们采取了许多方式尝试越境。1963年4月19岁的国家人民军的文职人员沃尔夫冈·恩格斯曾利用所在基地的苏联装甲运兵车冲破围墙,随后被东德边防军开火并击伤,最终被西德警察解救。托马斯·克鲁格曾利用东德体育技术协会的兹林Z 142轻型飞机穿越柏林墙降落在英国皇家空军位于加托的基地。另外有人通过挖地道、大型热气球、潜水以及利用汽车高速冲过检查站的方式越境。随后东德在检查站修筑了之字形的道路并降低了横杆的高度。由于下水道系统尚为柏林墙修建前的结构,部分人通过Girrmann学生组织的协助利用下水道越境。
附录大逃港
逃港,即逃亡至英属香港,中国大陆称“大逃港”,在香港又称为偷渡潮,是指在1950年代至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大量中国大陆民众尝试偷渡至英属香港之现象。自1951年中英封锁边界开始,共出现四次大规模的偷渡,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实行人民公社化期间;第二次是1961年开始,至三年大饥荒后1962年;第三次是1972年;第四次是1979年,大量人口逃港的原因,是为了摆脱贫穷和饥饿。逃港潮也促使并强化了英属香港的反共意识形态。
逃港者以最临近香港的广东人为压倒性多数,其次来自福建和四川(包括今重庆),后者比较多用合法途径。而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前后之移民以江浙(包括上海人)、山东、河南和天津为主。
由广东省偷渡来港者超过二百万,不少经香港移居东南亚或偷渡到欧美国家,按地区而言,最多是惠阳地区(包括今惠州市、深圳市、东莞市、河源市等)、潮汕、佛山地区,江门五邑地区以及广州,其次亦有数十万北方人以及华中人经上海偷渡到香港,少部分直接偷渡到香港,例如倪匡由内蒙古经上海偷渡到香港,李摩西以及李鹏飞亦从上海偷渡到香港,其余南方各省亦有零散数万人经广州偷渡到香港[3],总和亦有数十万,而南方人大多经广州、中山偷渡香港,北方人大多经上海及杭州偷渡到香港,所以现今香港人包括各省籍人。逃港而又成功者以男性较多,但亦有女性[注 1]。逃港者多为农民,亦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4]
逃港分为多个阶段,其中有因为中国大陆政府为了清除国内反动势力而任由逃离,但更多是因为忍受不了饥荒、阶级斗争等压迫。
逃港者以年轻人为主,大多因为香港和中国大陆有近百倍收入差距、认为香港遍地黄金(如电影《打蛇》的钻石山的谣传和《我的大嚿父母》之角色定位“抛妻别子偷渡去香港寻金觅财的康伯”)、向往香港生活等原因而逃港,逃港者亦有其他年龄层的人,因为被批斗、饥荒、希望赚取金钱以改善自己以及家人生活等原因到港,而年轻人则因为生活经验较浅,大多不是亲属被批斗而是希望赚取更多的金钱而到港。
大量人在偷渡过程中被鲨鱼咬死、游泳气力不足淹死、跳火车时摔死[5]、在偷渡过程中与解放军以及英国啹喀兵、华人兵纠缠中互有死伤、根据电影《打蛇》的资料搜集,不少人还遭被称为“打蛇人”的香港黑社会掳掠后强奸、斩杀[6],最后大约200万[7]至250万[8]成功越过边防线偷渡至香港市区,祇计1962年的大逃港,日均五千“大军南下”[9],短短一个月便南逃十五万人,著名事件包括华山救亲[10]。
1962年5月14日,由于逃港人数太多,香港政府决定放弃“安置难民”,开始“即捕即遣”涌入之难民[11]。约三万逃港者集结在香港上水华山,疲惫饥饿,在山中喘息,等候从市区闻讯赶来之亲人接下山。[12]
5月15日,金庸旗下《明报》发表了首篇社评:“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明报报馆一度成为救援物资中心。5月16日,胡仙旗下《星岛日报》刊登了《百名难民寄语香港亲友》一文。宗教团体、乡亲组织、新闻媒体发起了“援助有困难的人民”行动[13],前后共有十几万人次,送衣、送食、送水到华山。市民用各种方法保护华山上之亲友,包括接走、匿藏家中或市区。[14]
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下,警察将一批批越境者强行拖上卡车,送到石湖墟收容营地。当时香港政府决定,偷渡者在送入收容营后,免费给予两餐丰盛之自助餐,等第二日派车由罗湖桥送返大陆。当夜有市民守在营外,据报载:“滞留(在营外)的市民不下三四千众。”“他们当晚就在露天卧睡。”市内不少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都熄灯闭门,以示同情。
翌日,上万市民手持饼干、面包、粮袋,当卡车长龙驶出营门,公路两旁粮袋齐飞、泪雨倾盆。突然,成百人冲出马路,躺在地上,以身阻截车队,许多越境者纷纷跳车逃跑。
据事后估计,前后共有约过半华山越境者,在市民帮助及警察“抓捕不力”下,最后得以进入市区。[15]
在19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逐步取得中国大陆的控制权后最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相关的军政人员,以及资本家、地主、富农等为了逃避新政权,南下逃到英国殖民地香港。根据大陆官方档案显示仅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发的四次大规模逃港潮中,逃港者人数就达56万人。[16]。由于人数众多,香港政府在1950年5月起开始限制大陆人来港,并暂置国军家眷于调景岭[17];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因应抗美援朝,及为了清除国民党余党的需要,并没有封锁边境,任由他们离开中国大陆,直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才开始收紧边境。而同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大陆发动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大量仍留在大陆的资本家、地主、富农、以至于国民党中抗日人士被清算并受到批斗迫害,导致一些人在边境封锁后通过各种方式逃离大陆,揭开了逃港序幕。
1950年代初期,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不久,政局未稳、经济活动疲弱、民生凋敝;再加上政治运动四起,大跃进运动导致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田地颗粒无收,四五月份又青黄不接,大陆居民苦不堪言,迫切盼望逃出饥饿和高压的生活。[1]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大量知识分子、异见者因此被打成“右派”受到迫害,引发第一次大规模以知识分子为主的逃亡潮。1957年6月底至9月底,大陆公民第一次大规模通过宝安县(今深圳市)越境逃亡到香港,历时3个月遭到镇压而平息[1]。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引发了大饥荒,许多广东农民为了生存,纷纷外逃,广东地方政府起初对此默许,直至伊塔事件发生后政策才收紧。此后的逃港活动基本是非法经济移民以及家庭团聚。
1962年4月26日,在宝安县,大陆从惠阳、东莞、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来的公民结成长队伍,扶老携幼,牵儿带女,大量涌向香港,一日成功逃亡达到4,000人,参与逃亡人数8,000人,但是,51,395个来自12个省、62个县市的中国大陆公民被迫遣返。[1]1962年4月29日,宝安县公安局的14人假扮外流群众,混入逃亡人群,进行研究和考察,得知发起逃亡运动的主要是19岁到40岁的青壮年,尤其是大学生。[1]1962年5月6日,港英政府看到来势汹汹的人流,感到恐怖和震惊,于是将抓捕的逃亡者全部遣送回宝安。[1]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作出指示:“为了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中共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1]1962年5月22日,广东省的一万余官兵开始集中清理逃亡者,51395人被送返家中。[1]1962年6月19日,东莞县委发出指示,“对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干部、教师一律开除公职,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对参与外流的农村基层干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停止职务的处分。”[1]
1979年,深圳刚刚建市,香港即将在1980年实施即捕即解。因而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生了大规模越境逃亡香港的事件,人数共计十万余人,逃亡成功人数4万余人。[1]根据中国大陆官方资料,只计1979年广州的逃港失败而被捕入狱者已达5万,全省(尤以珠三角为主)达30万[18]。
更有资料显示,逃港者冒着极大生命安全风险,如水路(大鹏湾一带)常有鲨鱼出没、或会受到边防士兵开枪射杀。
而逃亡失败或者被遣返之中国内地居民,在被遣送回乡之后则会被视为“阶级敌人”,在批斗会上进行批判和殴打[1],并会被“劳改”(监禁和劳动刑罚)。
香港偷渡潮在世界史中,是冷战的一部分,国际上有称深圳河为“中国的柏林墙[21][22][23]”,是共产主义地区人民逃往资本主义地区“投奔自由”的世界史中之一部分[24]的评价。
因为珠三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成为其中一个主要移民地方,由珠三角偷渡到港的人口亦包括各省籍人口,包括当年占领广州的山东兵等。逃港亦大大加重了广东籍人口在香港人的比例,现今香港人口中的新移民有57%来自广东(包括先聚居在珠三角的各省籍人),这些人口又大多来自亲属移民,占总亲属移民的84%[26],香港的贫穷新移民人口几乎全为逃港者大陆亲属,其他省籍的移民以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为主。因为逃港者在中国大陆经历过批斗、饥荒的日子,他们比没有经历过中共统治、在香港出生的香港人更讨厌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大陆人,不少有恐共、反共、厌共甚至仇共的心态[27],对中共及香港本地亲共势力充满戒心和厌恶。故而不少香港人不接受香港主权移交,以及主张香港和中国大陆保持距离,并且很多都反对自由行和中港融合。不少中产在六四事件后到九七主权移交前亦大量移民外国,当时因为香港楼价高企,由香港移居外国的人口主要为投资移民,他们不少已经在1997年前售出楼宇,以投资移民外国[28]。
广东省因为与香港相距较近,许多试图逃港的居民都逃亡成功,造成了广东省人口锐减,工厂停办,城镇居民减少。[1]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广州市视察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1]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亦形容此事是“人民用脚投票”,将偷渡潮定性为经济原因而非政治原因。加上中国内地政府亦不想让偷渡潮持续而令其体面受损,为了阻止广东人民大量偷渡,决定让广东先富起来。最终,中国大陆1970年代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及1980年建立深圳经济特区,优先开放深圳、广州以及珠三角[31]。广州及深圳从此成为中国大陆富有地区,人民生活质素大大提升,再加上香港在1980年实施即捕即解,不再值得冒九死一生之风险偷渡来港。偷渡人潮大量减少同时,亦使其他省份人口大量移居广东[32],深圳最低工资亦是全大陆第一(2013年时达每月1600元),引来各省居民争相到深圳工作[33]。
当时,中国内地政府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曾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其中是如此描述:
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 香港黑社会横行; 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 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由于香港在1997年前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管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如大跃进、上山下乡及文化大革命影响不到香港,香港又处于经济腾飞时期,所以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事实上比中国大陆高出了许多。[35]
当时的饥荒导致云南边境居民偷渡到缅甸加入军阀部队谋生,在延边朝鲜族边民偷渡到北韩。1962年发生伊塔事件,大量新疆人偷渡苏联。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以司徒华为首的香港人士发起黄雀行动,秘密将民运人士营救至香港。北韩人通过各种方法偷渡和移居韩国(或其他地方),他们又被称为“脱北者”。
附录中印人均收入的对比
第3章 危机的解析
1929年中开始的那次经济萧条,对美国来说,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灾难。在1933年,经济降到最低点之前,以美元计算的国民收入减少了一半。总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失业人数上升到劳动力总人数的25%这一空前水平。这次萧条对于世界其他地方也是一场灾难。萧条逐渐扩及到其他国家,各国的产量下降,失业人数增加,人民遭受饥饿和苦难。在德国,萧条帮助了希特勒上台,铺平了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在日本,它加强了那个立志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军人集团。在中国,它导致了货币改革,这种改革最后加速了恶性通货膨胀,注定了蒋介石政权垮台的命运,使共产党上了台。
【按:我国的货币改革失败和当时美国财政部中的苏联间谍比如怀特很有关系!】
在思想上,萧条说服了公众,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注定要经受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公众转向了在知识分子中间已经越来越被接受的看法:政府应起更积极的作用;它应进行干预,抵消无节制的私人企业造成的不稳定;它应充当平衡轮,促进稳定和保证安全。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公众对私人企业和政府的作用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导致了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自那时起到现在的迅速扩大。
萧条也使经济学家的看法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经济的崩溃,动摇了那个长期持有并在二十年代曾得到加强的信念,即货币政策是促进经济稳定的有力工具。经济学家几乎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货币同经济稳定不相干”。二十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了另外一种理论。凯恩斯革命不仅俘虏了经济学专业,也为广泛的政府干预提供了吸引人的论据和处方。
公众和经济学家看法的转变,是由于误解了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却很少有人知道———萧条并不是私人企业失败所造成,而是政府在一个从一开始就被赋予责任的领域里的失败造成的。这个责任,用美国宪法第一款第八节的话来说,就是“铸造货币,调节它与外国货币的价值”。不幸的是,我们将在第九章中看到,政府管理货币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历史上的稀奇事,而且也是今天的现实。
联邦储备系统的起源
1907年10月21日,星期一,大约在一次经济衰退开始之后五个月,纽约市的第三大信托公司聂克波克信托公司开始遇到金融困难。第二天对这家银行的“挤兑”迫使它倒闭(结果证明是暂时的;它在1908年3月恢复了营业)。聂克波克信托公司的倒闭,加速了对纽约市内的后来也对全国其他地方的别的信托公司的挤兑——一次银行的“恐慌”发生了,就象在十九世纪不时发生过的那样。
不到一个星期,全国的银行对这种“恐慌”作出了反应,“限制付款”,也就是宣布它们不再付给要求提取存款的储户以通货。在某些州里,州长或司法部长采取措施,给予限制付款以合法的批准;在其他州里,干脆就容忍这种做法,银行被许可继续开业,尽管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它们违反了州的银行法。
限制付款遏制了银行的倒闭,结束了挤兑风潮。但这给企业带来了严重的不便。它导致硬币通货不足,使木质的分币在私下流通,并使其他暂时的代用品代替合法的货币。在通货最短缺时,得用一百零四美元存款买一百美元通货。恐慌加上限制,直接地和间接地使那次衰退变成了美国当时所经历的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所谓直接地,是指恐慌和限制对信心和有效地经营企业造成的影响,间接地是通过强使货币的数量减少。
不过,衰退的严重阶段为时不长。银行于1908年初恢复付款。几个月之后,经济开始恢复。这次衰退总共只持续了十三个月,而它的严重阶段只拖了大约一半那么久。
这一戏剧性的事件要对1913年通过联邦储备法负大部分的责任,它使得在货币和银行领域采取某些行动在政治上成为必要。在西奥多·罗斯福的共和党政府期内,建立了国家货币委员会,主席是著名的共和党参议员纳尔逊·W·奥尔德里奇。在伍德罗·威尔逊的民主党政府期内,著名的民主党众议员后来成为参议员的卡特·格拉斯重新草拟了该委员会的建议。从那以后,由此产生的联邦储备系统就成了国家管理货币的主要权力机构。
“恐慌”、“挤兑”和“限制付款”这些字眼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为什么它们会产生我们归因于它们的那些深远的影响?联邦储备法的作者又是怎样提议防止同样的事件的?
对一家银行挤兑,就是它的许多储户全都在同一个时间试图“提取”他们的存款。挤兑的发生,是由于有谣言或事实,使储户担心银行偿付能力不足,将不能履行它的义务。因而每个人都试图在存款还没有完全丧失之前把“自己的”钱取出来。
不难理解,为什么挤兑会使得一家偿付能力不足的银行更快地陷于破产。但是为什么挤兑也会给可信赖的和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带来困难呢?答案同英文里的一个最引人误解的字眼——“存入”有关,它被用来指对银行的一种要求权。如果你向一家银行“存入”通货,你往往会认为银行拿了你的钞票,把它们放进银行的保险柜里保存起来,等你来取款。它并不是这样做的。要是这样做的话,银行哪来的收入去偿付开支,去付存款利息呢?银行可能拿一些钞票放到保险柜里作为“储备”。其余的钞票它贷给别人,要借款人付利息,或者用于购买有息证券。
如果你存入的不是通货而是其他银行的支票(人们经常这样做),那么银行手头上就连可存入保险柜的通货也没有。它只有对另一家银行提取通货的要求权,而通常它并不行使这种权利,因为其他银行对它也拥有与此相当的要求权。对每一百美元存款,所有银行只在保险柜里存放几美元现金。我们实行的是“部分储备银行制”。只要人人都相信随时能够从存款中提取现金,因而只在真正需要时才提款,这种制度就能很好地运行。通常,新存入的现金大致与提取额相等,所以那一小部分储备就足以应付暂时的差额。但是要是人人都一下子取回现金,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多半会造成恐慌,就如有人在拥挤的戏院里喊“起火了”,每一个人都会赶紧往外跑一样。
如果只有一家银行碰到挤兑,那它可以从其他银行借款或是要求其借款人归还贷款来对付。借款人可以从别的银行提取现款来偿还贷款。但如果一场银行挤兑风潮扩大,银行是无法共同这样对付挤兑的。在银行的保险柜里干脆就没有那么多的通货,来满足所有储户的要求。此外,动用库存现金来对付广泛的挤兑——除非能立即恢复信任,结束挤兑,从而现金再次被存入银行——会使存款额大为减少。1907年,每一百美元存款,银行平均只有十二美元现金。每一美元存款换成现金从银行的保险柜转到存款人手里,需要另外减少七美元的存款,银行才能保持原来储备金同存款的比率。这就是为什么一场挤兑,结果使公众贮藏现金会减少总的货币供应量的缘故。这也就是为什么挤兑风潮如不立即终止会造成巨大痛苦的缘故。各个银行会催借贷户还债,拒绝延长贷款期限或拒绝发放新的贷款以取得现金,应付储户的要求。借贷户整个地告货无门,于是银行倒闭,企业破产。
如何能在一场恐慌一旦发生时就使之停止,或者更好的是如何能在它开始之前就加以防止呢?制止恐慌的一种办法,是象1907年那样:银行一起限制付款。银行仍然开业,但它们相互约定,储户提款时不付给现金,而是通过转帐来处理。对于自己银行的某一储户开给另一储户的支票,各银行的承兑方法是:减少前者帐下的存款,而增加给后者。对于那些由自己的储户开给其他银行的储户的支票或是由其他银行的储户开给自己银行的储户的支票,它们就几乎象往常那样,“经过票据交换所”来处理,也就是用所收到的其他银行储户的支票,抵消其他银行所收到的自己银行储户的支票。一个区别是,它们要付给其他银行的款项同其他银行要付给它们的款项之间的任何差额,是用支付保证来解决,而不是象通常那样拨付现金。银行也支付一些现金,不过不是付给要求提款的储户,而是付给一些老主顾,以供他们发放工资和其他紧急需要之用,同时银行也从这些老主顾那里得到一些现金。在这种制度下,某些“不殷实的”银行仍然可能倒闭。但它们倒闭,不是因为它们不能把殷实的资产转换成现金。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慌逐渐得到平息,对银行的信任得到恢复,银行又重新付款给提款的储户,而不致引起一系列新的恐慌。这是制止恐慌的颇为严厉的方法,但它确实起了作用。
另外一种制止恐慌的办法,是使殷实的银行能够把它们的资产迅速转换成现金,不是通过损害其他银行来转换,而是通过取得额外的现金——也可以说是通过紧急印刷机来转换。这就是体现在联邦储备法中的方法。据认为,该方法甚至可以防止限制付款引起的暂时混乱。根据该法建立的十二家地区银行,在华盛顿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督下营业,受权充当商业银行的“最后可以求助的放款者”。它们可以发放以下两种贷款,一种是以货币形式发放联邦储备券(它们有权印刷这种储备券),另一种是发放银行帐目上的存款信贷(它们有权创立这种信贷,只要薄记员把大笔一挥就行了)。它们充当银行家的银行。美国的地区银行相当于英格兰银行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
最初,人们预计,联邦储备银行的大部分业务是直接贷款给银行,以这些银行自己的资产,特别是以它们的期票即提供给企业的贷款为担保。但在许多这种贷款上,银行对期票进行“贴现”——也就是付出的款项比面值少,其折扣代表银行收取的利息。联邦储备反过来对期票进行“再贴现”,以此从银行收取贷款的利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开的市场活动”——即买卖政府公债——而不是再贴现,变成了联邦储备系统放松和收紧银根的主要方法。当一家联邦储备银行买进政府公债时,它支付联邦储备券(那是它保险柜里有的或者新印刷的),更通常的办法是,在它的帐本上为一家商业银行增加存款。这家商业银行可以自己是公债出售者,也可以是公债出售者保有存款户头的银行。这些额外的通货和存款就充作商业银行的储备,使它们整个能够成倍地扩大它们的存款,这就是为什么联邦储备银行的通货和存款被称为“高能货币”或“货币基础”的原因。当联邦储备银行售出公债时过程正好相反。商业银行的储备下降。它们被引向收缩。直到不久前,联邦储备银行创造通货和存款的权力,还受到联邦储备系统掌握的黄金量的限制。这个限制现在已被取消,所以今天除了负责这个系统的人的谨慎外,已不再有任何有效的限制。
三十年代初期,联邦储备系统未能做到建立它要做的事情之后,最后在1934年采取了一个防止恐慌的有效方法,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保证存款最大限度地不受损失。该保险公司使存款人相信他们的存款是安全的,因而防止了不殷实的银行的倒闭或金融困难造成对其他银行的挤兑。在那拥挤的戏院里的人们相信,再不会有火灾了。自1934年以来,虽然也曾有过银行倒闭和对个别银行的挤兑,但还没有发生过那种老式的银行恐慌。
早在1934年以前,为了防止恐慌,银行就已经常对存款进行担保了,只不过担保的范围较小,没有那么有效罢了。一次又一次,当一家银行碰到金融困难或是因为谣传发生问题而有挤兑危险时,其他银行就自动联合起来凑集一笔资金,为处于困难中的那家银行的存款担保。这种方法防止和阻止了许多恐慌。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或者是因为没有达成一项满意的协议,或者是因为没有立即恢复信心,该方法却没有奏效。关于这种失败,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考察一个特别富有戏剧性的重要事例。
联邦储备系统的早年
联邦储备系统于1914年底,欧洲爆发世界大战后的几个月,开始活动。这场战争大大改变了联邦储备系统的作用和重要性。
该系统建立时,金融世界的中心是英国。据说,当时世界建立在金本位制上,但同样可以说是建立在英镑本位制上。当初建立联邦储备系统,首先是为了防止银行恐慌并促进商业;其次是充当政府的银行。当时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将在世界金本位制的范围内活动,对国外事件作出反应,而不是去左右它们。
战争结束时,美国取代英国,成为金融世界的中心。世界有效地建立在美元本位制上,而且,即便是在战前的金本位制以一种削弱了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之后,也还是这样。联邦储备系统已经不再是一个被动地对国外的事件作出反应的无足轻重的机构。它已成了一个能够影响世界货币结构的独立的巨大力量。
战争期间,特别是美国参战后,不论是好还是坏,总之,联邦储备系统显示了其巨大力量。象在以前的(和后来的)战争中一样,为了筹措战费,印刷机又被派上了用场。不过,联邦储备系统使用印刷机的手法,要比以前的政府机构更为老练和隐蔽。联邦储备银行向财政部购买债券,用联邦储备券支付,使财政部能用储备券交付一些费用,只有在这时,才在某种程度上真正使用印刷机。在大多数情况下,联邦储备银行向财政部购买债券时,只是在帐册上给后者记一笔存款,以此作为付款。财政部用这些存款的支票支付它购买的东西。当支票接受人把支票存到他们自己的银行时,这些银行又把它们存到联邦储备银行,这样,财政部在联邦储备银行的存款就转给了商业银行,增加了它们的储备金。储备金的增加,使商业银行系统得以不断扩充,这种扩充在当时主要是通过它们自己购买政府公债或是贷款给它们的主顾使他们能够购买公债取得的。用这种办法,财政部得到了新创造出来的货币来支付战费,但增加的货币大都以商业银行存款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通货的形式出现。采用这种方法巧妙地增加货币数量,并没有防止通货膨胀,但它确实有神不知鬼不觉的作用,掩盖了实际发生的情况,减少或是延缓了公众对通货膨胀的担心。
战争结束以后,联邦储备系统继续迅速增加货币数量,从而助长了通货膨胀。但是在这一阶段,增加的货币不是用于政府开支,而是用于资助私营企业活动。我们整个战时的通货膨胀,有三分之一是发生在不仅战争结束而且政府的战争开支赤字也已结束之后。联邦储备系统很晚才发现它的错误。发现后,马上作出了强烈反应,把国家投入了1920-1921年为时不长但很严重的萧条。
无疑,联邦储备系统取得最大成功的时代,是在二十年代剩下的那段时间里。在那些年,它的确象一个有效的平衡轮似的起作用,当经济显露出摇摆的迹象时就提高货币的增长率,当经济开始以较快的速度扩张时就降低货币的增长率。它并没有使经济免于波动,但它的确缓和了波动。不仅如此,它是不偏不倚的,因而避免了通货膨胀。货币增长率和经济形势的稳定,使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当时有人大肆鼓吹说,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商业周期完蛋了,被一个警觉的联邦储备系统排除了。
【按:此时被称为“柯立芝(Coolidge)繁荣”,柯立芝执政策略:减税、降低政府开支、减少监管、加关税。由加关税可以看出美国并不是什么自由贸易的代表。】
二十年代的成就,大都应归功于一位名叫本杰明·斯特朗的银行家。此人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第一任行长,一直到1928年他突然病故时为止。在他死以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可以说是联邦储备系统执行的国内外政策的主要推动者,而本杰明·斯特朗无疑是最最关键的人物。他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正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所描述的,是“一个天才——银行家中的汉密尔顿”。同联邦储备系统内的其他人相比,斯特朗得到了该系统内部和外部金融界领袖们的更多信任和支持,他能够使金融界的领袖们相信他的看法,而且他有勇气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干。
斯特朗的死在联邦储备系统内部引起了权力之争,这场斗争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果。正如斯特朗的传记作者所说,“斯特朗的死使联邦储备系统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它失掉了一个有胆有识、深孚众望的领导人。〔设在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不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起那个作用。但该委员会自己又不能大胆地发挥那个作用,它当时仍然是软弱和分裂的……而且其他联邦储备银行大都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一样,不愿接受该委员会的领导。……因而,该系统陷入了遇事作不出决断、各方意见僵持不下的困难境地。”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权力之争竟然大大加速了权力转移,权力从私人市场转给了政府、从地方和州政府转给了联邦政府。事实证明,这场权力之争是权力转移的第一步。
萧条的开始
流行的看法是,大萧条开始于1929年10月24日。那天是星期四,天阴得非常厉害,纽约的证券市场崩溃了。其间经过几上几下,最后证券价格在1933年跌落到1929年那令人眩目的水平的六分之一。
证券市场的崩溃固然重要,但它并不是萧条的开始。企业活动在1929年8月,即证券市场崩溃前两个月就已达到了其顶峰,到10月时已经大大减少了。崩溃反映了经济困难的不断增加,反映了无法维持的投机活动的破产。当然,一旦发生崩溃,它就会在企业界人士和其他曾对新时代的到来寄予无限希望的人们中间散布疑虑。它使消费者和企业经营者都不愿花钱,而希望增加他们的流动储备以备急需。
联邦储备系统随后的做法,更加重了证券市场崩溃所造成的影响,危机进一步加深。当崩溃发生的时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几乎是出于斯特朗时代养成的条件反射,立即自行买进政府公债从而增加银行的储备,来缓和冲击。这使商业银行能够向证券市场上的公司提供额外的贷款,并从它们那里和其他受到崩溃的不利影响的公司那里买进证券,以缓和冲击。但是,斯特朗已经死了,联邦储备委员会想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它迅速行动,要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遵守纪律,后者屈服了。此后,联邦储备系统的做法就同它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早先的经济衰退中的做法大不一样了。它不是积极放松银根,使货币供应量多于平时,以抵消收缩,而是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听任货币数量慢慢减少。在1930年末到1933年初这段时间里,货币数量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一,与此相比,1930年10月前货币数量减少的幅度仍显得很小,仅仅减少了2.6%。不过同已往相比这个幅度却很大。的确,同以前的衰退相比,不论是在衰退期间还是在衰退之前,几乎哪一次货币也没有减少这么多。
证券市场崩渍的余波和1930年间货币数量的缓慢减少,最终导致了一场相当严重的衰退。即使那次衰退在1930年末或1931年初就告结束——如果不是发生货币崩溃的话,它本来很可能会是那样——它也会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衰退。
银行业的危机
但是,最坏的情况还在后头。直到1930年秋天,收缩虽然严重,但还没有发生银行业的困难或向银行挤兑的情况。当中西部和南部一系列银行倒闭破坏了人们对银行的信心并使人们广泛地想把存款变成通货时,衰退的性质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银行倒闭的浪潮最后蔓延到了全国的金融中心纽约。1930年12月11日是个非常关键的日子,那一天美国银行关了门。这是直到那时为止美国历史上倒闭的最大一家商业银行。此外,虽然它是一家普通的商业银行,它的名称却使国内外许多人认为它是官方银行。因而它的倒闭是对信心的特别严重的打击。
美国银行能起这样的关键性作用,是有几分偶然因素的。由于美国银行业的结构分散,加上联邦储备系统采取的政策是让货币储藏量减少而且不对银行倒闭作出有力反应,所以小银行的倒闭迟早会造成对其他大银行的挤兑。即使美国银行不倒闭,也会有其他大银行来诱发雪崩似的银行倒闭浪潮。是美国银行而不是其他银行倒闭,纯粹是偶然的巧合。它是一家殷实的银行。尽管它是在萧条最严重的几年里被清算的,但最后还是为每一美元存款偿付了九十二点五美分。无疑,如果它当时能挺住,储户一分钱也不会损失的。
当关于美国银行的谣言开始传播的时候,纽约州的银行总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纽约票据交换所银行协会曾试图制定一个计划挽救这家银行,为它提供保险基金或使它同其他银行合并。这是早先发生恐慌时标准的做法。直到银行关闭前两天,人们还认为这些努力一定能成功。
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了,主要是因为美国银行的特点加上银行界的偏见。它的名称本身,因为吸引移民,所以为其他银行所忌恨。更为重要的是,这家银行是犹太人拥有和经营,并主要是为犹太人服务的。它是在这一行业里少数几家犹太人拥有的银行之一,这个行业比几乎任何其他行业都更加照顾达官贵人。救助计划包括使美国银行同唯一另外一家纽约市内主要为犹太人所有和经营的大银行以及两家小得多的犹太人拥有的银行合并,不是偶然的。
计划失败是因为纽约票据交换所在最后一刻退出了所提议的安排——据说主要原因是一些银行界头面人物的反犹主义。在银行家们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纽约州银行总监约瑟夫·A·布罗德里克曾试图说服他们,但没有成功。他后来在法庭审讯时作证说,
“我当时说,它(美国银行)有许许多多借款人,它资助小商人,特别是犹太商人,它的关闭可能会使大批储户和借户破产。我警告说,它的关闭会使市内至少另外十家银行关闭,还可能影响储蓄银行。我告诉他们,关闭的影响甚至可能超出本市的范围。
我提醒他们,不过两三个星期以前,他们还拯救过市内两家最大的私人银行,曾经愿意提供所需要的资金。我回忆说,不过七、八年前,他们曾帮助过纽约的最大一家信托公司,提供的资金比拯救美国银行所需的数目要多许多倍,不过只是在制止了他们一些人之间的争吵之后。
我问他们,他们放弃这个计划的决定是否仍然不可更改。他们告诉我是这样。于是我警告他们,说他们正在犯纽约银行业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
美国银行关门,对它的所有人和储户来说都是悲剧。两个所有人受到审讯,据说违反了法律而被判处徒刑。储户的钱虽然最后得到部分偿还,但却被扣押了好多年。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后果更为深远。全国各地的存款人担心他们存款的安全,加入了早先已经开始的零星的挤兑活动。银行成批倒闭,仅1930年12月一个月,就有三百五十二家银行倒闭。
如果没有建立联邦储备系统,而发生挤兑风潮,那么,毫无疑问,银行会采取1907年采取过的措施,即限制付款,这种限制会比1930年最后几个月实际实行的要严厉得多。但是它会防止银行储备金的流失,几乎一定会防止后来1931、1932和1933年的银行大倒闭,正如1907年的限制很快就制止了当时的银行倒闭一样。的确,如果真是那样,美国银行也许会重新开业,就象聂克波克信托公司在1908年那样。恐慌过去,信心恢复,经济很可能在1931年初就开始复苏,就象在1908年初那样。
联邦储备系统的存在阻止了银行采取这种激烈的治疗措施:直接地是因为大银行的担心减少了,它们相信向联邦储备系统借钱可以使它们克服可能发生的困难,事实证明它们错了;间接地是因为整个社会特别是银行界相信,现在有联邦储备系统对付挤兑风潮,再不需要采取这种严厉的措施了。
联邦储备系统本来可以提供好得多的解决办法,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买进政府公债。这将为银行提供额外的现金以应付它们储户的要求。这会制止大批银行倒闭,至少是急剧减少倒闭的银行数目,防止公众把存款换成通货,从而不致使货币数量减少。不幸的是,联邦储备系统犹豫不决,采取的行动很少。总的来说它是袖手旁观的,听凭危机自由发展——在后来的两年中,它一再重复这种行动方式。
1931年春天,当第二次银行业危机来临时,联邦储备系统就是这样行事的。1931年9月,当英国放弃金本位制时,它甚至采取了更为反常的政策。联邦储备系统的反应是——在发生严重萧条两年以后——前所未有地大幅度提高利率(贴现率)。它采取这个行动是为避免持有美元的外国人来汲取它的黄金储备,这是它担心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提高利率,结果使国内的通货高度收缩——给商业银行和工商企业更增加了压力。联邦储备系统本来可以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政府公债,来抵消它给予正在挣扎的经济的这一剧烈打击,但它没有那么做。
1932年,在国会的强大压力下,联邦储备系统最后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买进债券。有利的影响刚开始被感觉到,国会休会了,而联邦储备系统立即就停止了它的计划。
这一惨痛故事的最后一段是1933年银行业的恐慌,又一次以一系列的银行倒闭开始。胡佛和罗斯福之间的交接班更加重了这次恐慌。罗斯福于1932年11月8日当选,但到1933年3月4日才就职。胡佛不愿意在未得到新当选总统合作的情况下采取严厉措施,罗斯福不愿意在他就职以前承担任何责任。
恐慌在纽约金融界蔓延开来,联邦储备系统自己也慌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试图说服胡佛总统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天宣布全国银行休假,但没有成功。他于是就会同纽约票据交换所银行和州的银行总监,说服纽约州长莱曼宣布全州各家银行在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职那一天休假。联邦储备银行与商业银行一起停业。其他州的州长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最后罗斯福总统在3月6日宣布全国休假。
中央银行系统的建立,最初是为了使商业银行无需限制付款,但后来它却同商业银行一道,对银行付款实行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无比广泛和完全的限制,严重地扰乱了经济。人们一定会赞同胡佛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的这样一句话:“我的结论是,它(联邦储备委员)在全国发生困难的时候,的确是一根不中用的稻草。”
在1929年中期经济处于顶峰时,美国有近二万五千家商业银行开业。到1933年早期,减少到了一万八千家。在罗斯福总统于银行休假开始十天后宣布其结束时,只有不到一万二千家银行获准开业,后来也只增加了三千家。因此,在四年的时间里,由于倒闭、合并或清算,在二万五千家银行中,总共大约消失了一万家。
货币的总量也同样急剧减少。如果1929年公众手头的存款和通货为三美元的话,那么到1933年就只剩下了不到两美元,真可以说是一次空前的货币崩溃。
事实和解释
这些事实今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事情,不过应当强调指出,当时的大多数观察家却没有看到这些事实,包括约翰·M·凯恩斯在内。人们可以对这些事实作不同的解释。货币崩溃是经济崩溃的原因呢还是结果?是联邦储备系统本来应该能够防止货币崩溃,还是象当时许多观察家得出的结论那样,联邦储备系统已经作了最大努力,但货币崩溃仍然不可避免?萧条是在美国开始然后扩及到国外呢,还是发源于国外而把美国国内本来可能是颇为温和的衰退加重了?
原因或结果
联邦储备系统本身对自己的作用没有任何怀疑。联邦储备委员会竭力为自己辩护,竟然在它的1933年《年度报告》中大言不惭地说:“联邦储备银行能够应付危机期间对通货的巨大需求,这显示了我国根据联邦储备法建立的货币制度的效能。……要不是联邦储备系统在公开市场上自由地购进债券,很难说萧条会怎么发展。”
货币崩溃既是经济崩溃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货币崩溃主要是联邦储备政策的,而它无疑加重了经济崩溃。经济崩溃一旦开始,又使货币崩溃恶化。银行贷款,在比较温和的衰退时期可能是“好的”贷款,但到了严重的经济崩溃时,就变成“坏的”贷款了。拖欠偿付贷款,削弱了发放贷款的银行,更促使存款人开始向它挤兑。企业倒闭,产量下降,失业增加——都加重不放心和担忧的感觉。把资产变换成其最流动的形式货币,变换成最保险的货币通货,成了广泛的愿望。“反馈”是经济制度的普遍特征。
现在,几乎已可确证,联邦储备系统不仅被授权防止货币崩溃,而且要是它把联邦储备法赋予它的权力运用得当的话,本来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这个系统的卫护者提出了一系列的借口。但其中没有一个经得起仔细推敲。没有一个足以说明,这个系统没有能完成它的创始人建立它所要完成的任务,是有道理的。联邦储备系统不仅有力量防止货币崩溃,而且也知道如何运用这个力量。在1929、1930和1931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曾反复敦促联邦储备系统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购进债券,这是联邦储备系统本应采取的关键性行动,但它没有采取。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并不是因为这些建议不对头或行不通,而是因为系统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得其他联邦储备银行和联邦储备委员会都不愿意接受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领导。结果只得受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混乱而犹豫不决的领导。该系统以外的有识之士也曾要求采取正确的行动。伊利诺斯州的议员A.J.萨巴思在众议院说:“我认定,解除金融和商业的困苦是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范围内的事。”某些提出批评的学术界人士——包括卡尔·鲍勃,他后来成为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在一次联邦储备会议上——这次会议在国会的直接压力下批准了1932年的公开市场购进——当时的财政部长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奥格登·L·米尔斯在说明他赞成那个行动时指出:“一个拥有70%黄金储备的大中央银行系统,在这样的形势下站在一边,不采取积极步骤,这几乎是不可想像、几乎是不可饶恕的。”然而这恰恰就是这个系统前两年的做法,而且在几个月后国会刚一休会以及在1933年3月最后银行危机达到高潮时,他又采取了这种做法。
萧条从哪里开始
萧条是从美国扩及世界其他地方而不是相反,这可以从黄金的流动情况得到肯定的证明。1929年,美国实行的金本位制规定了黄金的官价(每盎司二十美元六十七美分),按照这个价格,美国政府将应要求买进或售出黄金。多数其他大国实行的是所谓金汇兑本位制,它们也给黄金规定按它们自己的通货计算的官价。用美国的官价除以按它们的通货规定的黄金官价,便得出官方兑换率,也就是以美元表示的它们通货的价格。它们可以按照也可以不按照官价自由买卖黄金,但他们负责把汇率保持在按这两种黄金官价确定的水平,需要时按这个兑换率买进和售出美元。在这种制度下,如果美国的居民或其他持有美元的人在国外花费(或借出或赠送)的美元,比接受这些美元的人愿意在美国花费(或借出或赠送)的多,那么,后者就会用多余的美元兑换黄金。黄金就将从美国流向外国。如这差额是相反方向的,持有外国通货的人想在美国花(或借出或赠送)的美元,比持有美元的人愿意兑换外国通货在国外花(或借出或赠送)的多,那么,他们可以向他们的中央银行按官定兑换率购买额外的美元。他们的中央银行将把黄金送到美国以得到这额外的美元。(当然,实际上这种交换并不需要真的远渡重洋运送黄金。外国中央银行拥有的黄金,有许多就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金库里,加有所属国家的“标记”。转换的时候只要改变华尔街地区自由大街33号银行大楼地下室深处盛放金条的容器上的标签就行了。)
如果萧条是起于国外,而美国经济在一段时间里继续繁荣,那么,国外恶化的经济情况会减少美国的出口,而外国货的价钱降低,会鼓励美国进口。结果会是想在国外花(或是借出或赠送)的美元,要比接受者想在美国花的多,这样黄金就从美国流出。黄金的流出会减少联邦储备系统的黄金储备,从而促使联邦储备系统减少货币数量。固定汇率制就是这样把通货收缩(或通货膨胀)的压力从一个国家转移给另一个国家的。如果当时情况是这样,那么联邦储备委员会会理直气壮地说,它的行动是为了对付外来压力的。
反过来,如果萧条起于美国,那么最初的影响就会是持有美元的人想在国外花的美元数目减少,而其他人想在美国花的美元数目增加。这会使黄金流进美国,从而迫使外国减少它们的货币数量,这样,美国的通货收缩就转移给了外国。
事实是清楚的。从1929年8月到1931年8月,即通货收缩的头两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增加。这确凿地证明,美国是萧条的发动者。如果联邦储备系统遵循金本位制的原则,那它应当增加货币的数量来对付黄金的流入。相反,它实际上却听凭货币的数量减少。
一旦萧条发生并传给其他国家,自然就会对美国产生反作用。这是又一例证,说明复杂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着反馈作用。处在一场国际运动前列的国家,并不一定永远处在前列。法国1928年重新实行金本位制后,所规定的兑换率使法郎贬值,因而积聚了一大笔黄金。所以它完全能够抵挡来自美国的通货收缩的压力。可是法国执行了甚至比美国还严厉的通货紧缩政策,不仅开始增加它的本来已经很多的黄金储备,而且,从1931年末起开始从美国收购黄金。它发挥这种领导作用所得到的报酬是,虽然美国经济在1933年3月降到最低点,停止支付黄金,法国的经济却直到1935年4月才达到最低点。
对联邦储备系统的影响
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好心劝告而执行反常的货币政策,其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之一是,在同纽约和其他联邦储备银行争权的斗争中,该委员会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当时流传的神话是:私人企业包括私人银行系统失败了,政府需要更多权力以对付据说是自由市场固有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储备系统的失败,产生了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得以对地区银行进行更多的控制。
这种变化的象征之一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从美国财政部大楼里的朴素的办公处迁到了宪法路它自己的一座堂皇的希腊庙宇里(从那以后又加建了巨大的建筑)。
这场权力转移的最后一个标志是,改变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名称和地区银行负责人员的称号。在中央银行圈子里,受尊敬的称号是行长而不是总经理。从1913年到1935年,地区银行的头头称作“行长”;华盛顿的中央机构叫作“联邦储备委员会”,只有该委员会的主席称“行长”,其他成员就叫“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1935年的银行法把这些都改了。地区银行的头头不再叫“行长”,改叫“总经理”,而“联邦储备委员会”这个紧凑的称呼改成了臃肿的“联邦储备系统行长会议”,只是为了使每一个成员都有“行长”称号。(译注:“联邦储备系统行长会议”的习惯译法是“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总经理”亦译“行长”。这里为了便于看清其(改变的意义,故改成以上译法。)
不幸,增加权力、威望和办公处的装璜并没有相应改善工作。自1935年以来,这个系统主持了——而且大大促进了——1937-1938年的大衰退、战时和战后的通货膨胀以及从那时以来起伏不定的经济,通货膨胀时高时低,失业时增时减。每一次通货膨胀的高峰和每一次暂时的通货膨胀低落点。都一次比一次高;平均的失业水平也逐渐升高。该系统没有再犯它在1929-1933年犯的那种错误——容许或促进一场货币崩溃——但它犯了相反方面的错误,促使货币数量过分迅速地增加,这就助长了通货膨胀。此外,它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不仅制造景气,而且也制造不景气,有些是温和的,有些是剧烈的。
该系统只在一个方面完全保持始终如一。它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非它所能控制的外部影响,而把所有有利的情况都归功于自己。它就是这样继续助长那个说私人经济不稳定的神话,而它的行为则继续证明这个现实:政府是今天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本节内容概述
本节回顾美联储的早期历史,证明美联储是美国大萧条的罪魁祸首。
该系统只在一个方面完全保持始终如一。它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非它所能控制的外部影响,而把所有有利的情况都归功于自己。它就是这样继续助长那个说私人经济不稳定的神话,而它的行为则继续证明这个现实:政府是今天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附录:中国货币改革失败和美国、苏联的关系
1953年真纳和麦卡锡的指控
参议院威廉·真纳领导的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SISS)对政府部门进行的内部连环彻查中对非民选官员行使未经授权和不受控制权力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调查,特别是针对怀特。得出报告中的部分是关于罗斯福政府施行的中国政策,以《摩根索日记(中国)》为名出版。报告称:
“财政部中特别是财金研究部里聚集了大量共产党同情者,这是创下纪录的事实。怀特是该部门的第一任主管,继承他的主管是柯福兰和哈罗德·葛莱瑟。受雇于财金研究部的有威廉·路德维格·乌尔曼、厄尔文·卡普兰和维克托·佩洛。其中,怀特、柯福兰、葛莱瑟、卡普兰、佩洛都被认定为共产党阴谋组织的成员……”
委员会还听取了亨利·摩根索的演讲撰写人乔纳森·米歇尔的证词,指出怀特试图说服他苏联已经发展出一套可以取代资本主义和基督教的体系。
1953年,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司法部长小赫伯特·布朗内尔公布了在杜鲁门总统任命怀特任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联邦调查局给政府当局发出的警告。布朗内尔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5年11月8日写给白宫的信,其中对怀特及其他人发出了警告。这显示白宫在杜鲁门提名怀特任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六周之前就已收到联邦调查局题为《苏联在美间谍活动》的报告,其中就包括怀特的案件。
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在1997年莫伊尼汉委员会报告中就政府保密问题写下的引言中,尽管不否认联邦调查局向杜鲁门发出许多此类警告,但指出杜鲁门始终未被告知关于维诺那计划的情况。为证明此点,他引用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撰写的维诺那计划官方历史中的一则声明称“没有明显证据能够证明”杜鲁门总统知晓维诺那计划。
维诺那计划
国安局的密码学家认定哈里·迪克特·怀特就是维诺那计划破解密电多次提到的消息来源,其行动代号有“律师”、“理查德”和“陪审员”。在他死后两年,在一份1950年10月15日成文的备忘录中,怀特被联邦调查局根据维诺那计划收集的证据认定为苏联线人,行动代号“陪审员”。
数年后,司法部公开了维诺那计划,其中破解的苏联有线电报里以“陪审员”指代苏联线人怀特。联邦调查局就怀特提交的备忘录中报告称:
“您此前已经收到从(维诺那计划)中搜集到的关于‘陪审员’的情报,此人活跃于1944年。根据(维诺那计划)之前收到的关于‘陪审员’上交的情报,1944年4月间他提交了关于时任国务卿赫尔同副总统华莱士之间对话的报告。他还报告了华莱士的中国之行。1944年8月5日他向苏联报告称他坚信除非有一场重大军事失利,罗斯福能够在即将到来的的选举中获胜。他还报告说选择杜鲁门担任副总统是考虑到要保证民主党保守派的选票。据报告称,‘陪审员’很愿意为克格勃做出任何个人牺牲,但他担心他的行为一旦曝光会造成政治丑闻,对选举会有影响。”
这一代号被克格勃档案员瓦西里·米特罗欣的笔记证实,其中点出了六名关键性苏联特工的名字。哈里·迪克特·怀特位列其中,其代号一开始是“卡西尔”后来是“陪审员”。
怀特作为帮助苏联发挥影响力的特工的另一个例子就是他在1943年阻挠了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一笔已许诺的两亿美元贷款,他所收到的指令要求在通货膨胀上升至不可控制之时就要执行这笔贷款。
另一些维诺那破解密电显示出对怀特更加不利的证据,包括怀特向他的苏联递信人建议如何碰头和传递信息。维诺那档案71号破解密电包含了怀特讨论为他给苏联所做工作应得的报酬。
1997年,由民主党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担任主席的跨党派有关政府保密事务的莫伊尼汉委员会公布其结论:“关于国务院的阿尔杰·希斯的复杂案件已经可以定案,财政部的哈里·迪克特·怀特亦是如此。”
苏联档案员和克格勃工作人员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披露了关于怀特充当苏联特工行为的复杂性的更多证据。在其与阿兰·韦恩斯坦所著的《闹鬼的森林:苏联在美间谍活动——斯大林时代》(The Haunted Wood: Soviet Espionage in America — the Stalin Era)中,作为前苏联记者和克格勃工作人员的瓦西里耶夫公布了关于怀特为苏联做事的相关苏联档案。怀特坚持把财政部职员、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间谍哈罗德·葛莱瑟“提拔并保留在财政部,尽管知晓他的共产党背景”。有怀特撑腰,葛莱瑟通过了联邦调查局背景调查。1941年12月秘密情报部门向哈里·怀特提出报告指出有证据表明葛莱瑟参与了共产党活动。怀特从未回应这份报告。葛莱瑟继续供职于财政部,很快开始招募其他特工,并开始给苏联内政部提供有关财政部人员和其他潜在间谍人选的简报。在美国参加二战以后,葛莱瑟在怀特的批准下得以得到政府部门中几个更高职位的任命。
根据苏联档案,怀特的其它克格勃代号有“理查德”和“里德”。为了保护这一线人,苏联情报部门经常更换怀特的行动代号。
附录: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第一代凯恩斯男爵(John Maynard Keynes, 1st Baron Keynes,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一般称作凯恩斯(或译为凯因斯),英国经济学家。
凯恩斯一反自18世纪亚当·斯密以来尊重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预的经济学思想,他主张政府应积极扮演经济舵手的角色,透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对抗经济衰退乃至于经济萧条。
凯恩斯的思想不仅是书本里的学说,也成为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世界性经济萧条时的有效对策,以及构筑起1950年代至1960年代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繁荣期的政策思维,因而被夸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或译救世主)”、“战后繁荣之父”等。一度主宰资本主义的凯恩斯思想也成为经济学理论与学派之一,称为“凯恩斯学派”,并衍生数个支系,其影响力持续至今。
凯恩斯可谓经济学界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发表于1936年的主要作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起了经济学的革命。这部作品使人们对经济学和政府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凯恩斯发展了关于生产和就业水平的一般理论。其具有革命性的理论主要是:
- 关于存在非自愿失业条件下的均衡:在有效需求处于一定水平下的时候,非自愿失业是可能的。与古典经济学派相反,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无法解决非自愿性失业问题。
- 引入不稳定和预期性,建立流动性偏好倾向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投资边际效应概念引入推翻了萨伊定律和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
他的这些思想为政府干涉经济以摆脱经济萧条和防止经济过热提供了理论依据,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凯恩斯一生对经济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曾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不过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的政策也带来停滞性通货膨胀,因此也称他为“战后滞胀病之父”。
新凯恩斯学派是20世纪50、60、70年代时,部分经济学家为应对第一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挑战而提出的。差异有以下二点:
- 保罗·萨缪尔森等新凯恩斯学派学者把国家干预不只视为为应对经济危机的应急措施,而当作调节经济的基本手段,主张在萧条时采用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在繁荣时采用紧缩性政策抑制经济,以求让经济平稳发展。
- 新凯恩斯学派除了凯恩斯学派一様重视财政政策外,也主张同时调整货币政策,以对经济的刺激更为有力。
新兴凯恩斯学派是劳伦斯·鲍尔、格里高利·曼昆、戴维·罗默、奥利维尔·布兰查德、乔治·阿克洛夫、珍妮特·耶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时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经济出现了“滞胀”现象,新凯恩斯学派由于无法解释该现象受到了怀疑,因此经济学家们提出了新兴凯恩斯学。主要特色是基于工资粘性和价格粘性展开分析,它假设名义工资和产品价格是可以调整的,但是调整速度十分缓慢。
虽然凯恩斯经常被视为热衷于改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社会主义者,他曾表达对资本主义的失败可能会迫使公众转向社会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一事的担忧,而且凯恩斯的一些作品表达了他对改革资本主义制度一事的期望和对于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反感,他曾多次抨击马克思社会主义丶 表示他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荒唐的和乏味的,它从未合理地解释为何会出现经济动荡,而且除了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之外,它从未提出任何有效的建议,并且声称《资本论》是过时的、错误的和毫无用处的,这些言论表明凯恩斯从未认真地审视过马克思的思想,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简化为只主张让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的地位的马克思社会主义以对其进行稻草人论证,但是经济学家加里·蒙吉奥维(Gary Mongiovi)教授认为凯恩斯事实上并不拥护资本主义,而是希望以自由社会主义来取代其地位,但凯恩斯对将来社会的设想是否属于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仍有很大的争议性,而且不像不少反共产主义者所描述的那样,凯恩斯本人十分反对斯大林主义。经济学家爱德华·富勒(Edward W. Fuller)研究了与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有关的文献,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 凯恩斯本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
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及芝加哥派人士曾经公开抨击凯恩斯主义。拥护放任自由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亨利·赫兹利特曾经声称凯恩斯在其著作《通论》中所提出的理论没有一个是真实而原创的。
与凯恩斯的理念相对,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前者的论点都是错误、具有误导性的,他指出凯恩斯的理论仅仅在特殊情况下才能成立。例如,凯恩斯假设货币的周转速度是一定的,个人或企业短期内无法加以改变此宏观经济。而熊彼特指出所有现实迹象都与这种假设相反。时至今日所试行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不管是原始的凯恩斯主义还是被弗里德曼修正了的凯恩斯主义,都已经被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击败。再例如,凯恩斯认为通过操纵几个简单的货币关键因素—政府开支,利率,信贷量或货币流通量就可能维持就业水平和经济繁荣稳定的永久性均衡,但熊彼特的认为符号经济作为主导经济的出现 ,反而打开了通向专制的大门。另外,熊彼特还将凯恩斯所忽略的经济体系“外面”的“边缘”的因素“创新”,作为经济体系真正的核心因素来对待。两位20世纪最负盛名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在经济原理及政治观点上皆可见一斑。
凯恩斯经济学(英语:Keynesian economics),或凯恩斯主义(英语:Keynesianism),凯恩斯理论(英语:Keynesian theory),是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政府应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透过增加总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总体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总体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凯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总体经济学,与以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个体经济学相区别。
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自动机制。这与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依定律相对,后者认为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试图将总体经济学和个体经济学联系起来的努力成了凯恩斯《通论》以后经济学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一方面个体经济学家试图找到他们思想的总体表达,另一方面,例如货币主义和新兴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试图为凯恩斯经济理论找到扎实的个体基础。二战以后,这一趋势发展成为新古典主义综合。
第4章 从摇篮到坟墓
1932年的总统选举是美国政治上的分水岭。争取再次提名为共和党候选人的赫伯特·胡佛面临着严重的萧条问题。数百万人失业。排队领取救济食品,失业者站在街头卖苹果,成了这一时期的标准写照。虽然责任是在独立的联邦储备系统,是它的错误的金融政策使衰退变为灾难性的萧条,然而,作为一国元首的总统,也不能推卸责任。公众丧失了对整个经济体制的信心。人们感到绝望,需要得到一个能够摆脱困境的保证。
民主党候选人是具有超凡魅力的纽约州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作为一位新人,他洋溢着希望和乐观情绪。果然,他按老章程竞选,许诺说要是他当选,将解决政府的浪费,平衡预算,并指责胡佛政府开支无度,听任国家赤字上升。另外,在选举前和就职前的交接班期间,罗斯福经常在奥尔巴尼的州长官邸与他的一伙被称为“智囊”的顾问们碰头。他们制定了罗斯福就职后要执行的措施,后来就形成罗斯福在接受民主党候选人提名时,向美国人民保证要奉行的“新政”。
1932年的总统选举,仅仅就其政治意义来讲,也堪称为分水岭。在1860至1932年的七十二年中,共和党执政五十六年,民主党十六年。在1932到1980年的四十八年中,纪录颠倒了过来,民主党执政三十二年,共和党十六年。
这次总统选举还在一种更为重要的意义上是分水岭。它标志着在公众眼中政府应有的作用和实际上赋予政府的作用的巨大变化。其变化之大可从一组简单的统计数字中看出。自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到1929年,各级政府的开支(包括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除遇重大战事,从未超过国民收入的12%。而且,其中三分之二是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联邦的开支通常只占国民收入的3%或更少。然而,自1933年起,政府开支从未低于国民收入的20%,而目前已超过40%,其中三分之二是联邦政府的开支。不错,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冷战或热战中度过的。然而自1946年以来,光是非国防开支就从未低于国民收入的16%,目前大约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仅联邦政府开支一项就已超过国民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而光是非国防开支就已超过五分之一。靠这种方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联邦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扩大了大约十倍。
罗斯福是在1933年3月4日,即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刻就任总统的。许多州宣布了银行停业。罗斯福就职两日后,下令关闭全国所有银行。但是,罗斯福借就职演说的机会,向全国发表了一篇鼓舞人心的演说。他说:“我们唯一该恐慌的是恐慌本身。”接着。他就发起了一场狂热的立法活动,即所谓国会特别会议“一百天”。
罗斯福的智囊团的成员,主要来自大学,特别是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反映了在这以前已经在校园内的知识分子中间发生的变化,即从信仰个人负责、自由放任和权力分散的、有限的政府,转到信仰社会负责和集权的、强有力的政府。他们认为,政府的职能在于保护个人不受不测风云的影响,并根据“总的利益”来控制经济活动,即便是需要政府来拥有和运用生产资料也罢。这两条原则,早在爱德华·贝拉米1887年发表的著名小说《回顾》中就已提出来了。在那个乌托邦式的幻想小说中,有一位叫里普·范·温克的人物。他一觉从1887年睡到2000年,醒来时发现世界变了样。在“回顾”时,他的新同伴们向他解释了那个令他吃惊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预言的日期——的乌托邦是怎样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苦难中出现的。那个乌托邦就包括了许诺“从摇篮到坟墓”(我们第一次碰上这个词)的保险,以及详尽的政府计划,其中有一规定,所有的人有义务为国家服务一段时间。
【原书按:应该把出现这些词语的整个句子引录下来,因为它十分精确地描述了我们正在走的道路,并无意中暗示了由此造成的后果。原话是这样说的:“再也没有人为自己的未来或是儿女的未来担心了,因为国家为每个公民一生担了保,他们将得到良好的抚养和教育并将过舒适生活。”爱德华·贝拉米:《回顾》(纽约:现代丛书公司,1917年;1887年第1版),第70页。】
罗斯福的顾问们都来自知识界,因而自然把这次萧条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并认为,政府,特别是中央集权政府的积极干预才是对症良药。仁慈的政府官员和无私的专家们,应当从狭隘、自私而又“保守的实业界巨头”手里接管他们滥用的权力。用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的话来说,“货币兑换商从我们文明圣殿的宝座上逃走了。”
顾问们在制定罗斯福的纲领时,不仅能从校园中,而且还从过去俾斯麦的德国、费边的英国和介乎于二者之间的瑞典的经验中得到借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产生的“新政”,明显地反映了这些观点。它包括一些旨在改革基本经济结构的计划。有些计划在最高法院宣布它们为非法之后不得不放弃,最明显的是放弃了建立国家复兴署和农业调整署的计划。其他计划则照旧执行:建立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在全国规定了最低工资限额。
“新政”还包括一些灾祸保险计划,主要有社会保险(老年和遗属保险)、失业保险和政府补助。本章将论述这些措施及其后果。
“新政”还包括一些完全临时性的计划,以对付大萧条带来的紧急情况。这些计划既然是政府计划,因而毫不奇怪,其中一些临时性计划后来就变成了永久性计划。
【按:政府临时执行的紧急性政策应设定一个相对明确的结束时间或标准,例如军政、训政,又如作为临时性措施的九品中正制和两税法。】
最重要的临时性计划有:“创造就业机会”(该计划由工程进度管理署执行),利用失业青年改善国立公园和森林(该计划由地方资源养护队执行),以及联邦政府直接向贫困者提供救济。这些计划的确发挥了作用。当时人们的情绪普遍都很沮丧,迅速采取某种行动来消除这种情绪,帮助陷于苦难中的人们并恢复公众的希望和信念,是重要的。这些计划制定得很仓促,无疑是不完善、不经济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罗斯福政府在消除当时的沮丧情绪和恢复公众信任方面,颇有成效。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新政”,但同时大大加强了它的基础。战争带来了庞大的政府预算以及政府对具体经济生活的前所未有的控制:通过法令规定物价和工资,实行消费品配给,禁止某些民用品的生产,分配原料和成品,以及控制进出口。
失业现象的消灭,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军火库”的战争物资的大量生产,以及使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所有这一切表明,同“无计划的资本主义”相比,政府能够更有效地管理经济。战后通过的主要法令之一是1946年的“就业法”。该法令表达了政府在维特“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方面的责任。这实际上是把凯恩斯的政策变成了法律。
战争对公众态度的影响与萧条所产生的影响极为相同。萧条使人们相信资本主义有毛病;战争使人们相信中央集权的政府是有效的。其实,两种结论都不正确。萧条是由于政府的无能造成的,而不是由于私人企业。在战争中,为了一个压倒一切的目的,政府可以暂时行使巨大的控制权。这个目的是几乎全体公民所共有的,他们都乐于为它作出重大牺牲。而政府为促进含糊不清的所谓“公共利益”永久控制经济,则是另一回事。这个“公共利益”是由公民们的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愿望构成的。
战争结束时,中央规划经济似乎成了未来的潮流。其结果受到一些人的衷心欢迎,他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新世界的黎明,大家将平等地分享富裕生活。其他人,包括我们在内,则是同样衷心地感到恐惧。在我们看来,它是走向专制和苦难的转折点。迄今为止,无论是前者的希望还是后者的恐惧,都没有成为现实。
政府的作用扩大得多了。然而,这种扩大并没有采取我们许多人曾经担心的那种形式,即中央制定具体经济计划,并对工业、金融和商业实行愈来愈广泛的国有化。人们根据以往的经验不再制定具体的经济计划了,部分地是由于它未能成功地实现已宣布的目标,同时也是由于它与自由的原则相冲突。这种冲突明显地表现在英国政府企图支配人民就业上。公众的反抗迫使政府放弃了这种企图。英国、瑞典、法国和美国的国有化工业效率极其低下,亏损额极其巨大,以致今天只有少数顽固不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认为进一步国有化是可取的。一度曾广泛为人接受的,以为国有化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幻想破灭了。诚然,现在政府有时仍然对个别部门和企业实行国有化,如美国的铁路客运和部分货运、英国的雪兰汽车公司以及瑞典的钢铁业。但实行国有化的原因却大不相同:有的是由于市场情况要求削减服务,但消费者希望予以保留,由政府补贴;有的是由于无利可图的企业的工人害怕失业。甚至那些支持这种国有化的人们,也不过是将它看成是不得已的事情。
计划和国有化的失败,并没有解除要求建立更为庞大的政府的压力,只是改变了压力的方向。政府的扩张现在采取了实行福利计划和开展调节活动的形式。正如W·艾伦·沃利斯用另一种说法所阐述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关于生产手段社会化的论据一个又一个地被戳穿,在理论上破产了,现在又谋求生产结果的社会化。”
在福利方面,方向的改变导致了最近数十年福利事业的激增,特别是在1964年林顿·约翰逊总统宣布“向贫穷开战”之后。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和直接救济等“新政”时期实行的计划,扩及到了新的集团;付款额增加了;增添了医疗照顾、医疗补助、食品券和其他许多计划。公共住房和城市复兴计划也扩充了。现在总共有数以百计的政府福利和收入转让计划。1953年,为把零散的福利计划集中起来,建立了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开始时预算为二十亿美元,不到国防开支的5%。而二十五年后的1978年,它的预算达到一千六百亿美元,为陆海空三军总开支的一倍半。它的预算之大在世界上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政府的预算和苏联政府的预算。该部管辖着一个庞大的王国,渗透到全国的每个角落。国内每一百名雇员中就有一名以上受雇于这个卫生、教育和福利王国,不是直接为该部服务,就是为由该部负责的、但由州或地方政府机构执行的计划服务。我们大家都受到了其活动的影响。(1979年底,从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分离出了一个教育部。)
谁也解释不了下面这样两个表面上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是人们对福利事业激增的后果普遍不满;一是人们继续施加压力要求进一步扩大福利事业。
目标都是崇高的,结果却令人失望。社会保险开支剧增,政府在财政上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公共住房和城市复兴计划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提供给穷人的住房。尽管就业人数不断增加,但接受公共补助的名单却越来越长。普遍一致的看法是,福利计划一团糟”,充满弊端和腐化。全国大部分医药费用由政府支付后,病人和医生却都抱怨开支剧增,抱怨医疗越来越缺少人情味。在教育方面,随着联邦政府干预的扩大,学生的成绩不断下降(见第六章)。
这些好心的计划接连遭到失败,并非偶然,也不单单是因为实施方面的错误所造成。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用恶劣的手段来达到良好的目的。
尽管这些福利计划失败了,然而,要求扩大这些计划的压力却有增无减。有人把失败归咎于国会在拨款时太小气,因而呼吁实施更广泛的计划。某些计划的得益者为进一步扩大这些计划而施加压力,其中首先就是实施这些福利计划的大批官僚。
一个吸引人的代替当前福利制度的办法是,向收入低于法定标准的家庭提供联邦补助。这个主张得到了具有各种不同政治信仰的个人和集团的广泛支持。目前已有三位美国总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然而,这种建议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似乎难以在政治上付诸实施。
现代福利国家的出现
最早大规模采用福利措施(这些措施现在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普遍采用)的现代国家,是“铁面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统治下的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提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社会保险方案,向工人提供事故、疾病和老年保险。他的动机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出于对下层群众的家长式的关心,同时也是狡猾的政治手腕。他的措施是用来破坏当时刚刚出现的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吸引力的。
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那样的一个本质上是贵族独裁的国家(用今天的行话来说就是右派独裁国家),竟会带头采用通常只有社会主义和左派才会采用的措施,似乎是咄咄怪事。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即使撇开俾斯麦的政治动机,也是如此。专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徒们都信奉中央集权,信奉靠命令进行统治,而不靠自愿合作。他们的分歧在于由谁来统治:是由血统决定的杰出人物来统治,还是由择优而取的专家来统治。他们都非常真诚地宣称,他们想要提高“全体大众”的福利;宣称他们知道什么是“公共利益”,而且知道怎样才能比一般人更好地为其服务。为此,他们都宣扬家长式的哲学。但是,一旦掌权,他们就都会在“全体福利”的幌子下,为其本阶级谋利益。
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保险措施更为接近的先例是英国采用的措施。这些措施始于1908年通过的养老金法和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
养老金法规定给予任何年过七十、收入低于规定数额的老年人以周养老金,金额按领取者的收入情况而定。它绝非捐助性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直接救济,即在英国存在了数百年的济贫法的延续。然而,正如A.V.迪塞指出的,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养老金被认为是一种权利。用养老金法中的话来说,不能因为领取养老金而“剥夺人们的任何公民权、权利或特权,也不能因此而使人们丧失任何资格”。养老金法颁布五年后,迪塞在评论该法令时写道:“一个乐善好施的聪明人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领取养老金也即救济金的人依然有权参加下院议员的选举,这种规定是否将对整个英国有利。”当时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谁也不会感到奇怪,但现在如果接受政府的慷慨赐与意味着丧失选举资格,那就是打着灯笼也不会找到一个有选举资格的人。这说明我们在福利国家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多么远。
国民保险法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第一,给所有受雇于联合王国的年龄在十六至七十岁之间的人保健康险,即保证他们有钱看病;第二,给受雇于该法令规定的那些部门的人保失业险,即保证他们在失业期间得到补助。”与养老金不同的是,国民保险法是捐助性质的,它的资金由雇员、雇主和政府共同负担。
由于它是捐助性质的,也由于它着眼于防止意外事故,该法令甚至比养老金法还要激进,更离开了以前的做法。迪塞写道:
根据国民保险法,国家招致了新的、可能是很沉重的负担。而挣工资的人则得到了新的、很广泛的收益。……在1908年以前,一个人不论贫富,是否为自己的健康保险,完全是每个人自由定夺的问题。他的选择同他要穿一件黑色上衣还是一件褐色上衣一样,与国家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国民保险法到头来会给国家,也就是给纳税人带来比英国选民们所预料的要沉重得多的责任。……失业保险……实际上是国家承认自己有责任使每一个人免受失业之苦……国民保险法正符合社会主义的理论。它与自由主义,甚至与1865年的激进主义很不协调。
美国早期的这些措施,同俾斯麦的措施一样,表明了贵族统治与社会主义的相近之处。1904年,温斯顿·丘吉尔脱离贵族的保守党,加入了自由党。他作为劳合·乔治内阁的成员,在制定社会改革的法令方面起了主导作用。改换政党(后来证明只是暂时的)并不象半个世纪以前那样,需要改变原则,半个世纪前,自由党对外实行自由贸易,对内实行自由放任主义。他所提出的社会立法,虽然在范围和种类上同以前的立法有所不同,但还是继承了家长式工厂法的传统。该法令是十九世纪主要在所谓的激进保守党人的影响下通过的。这批激进保守党人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贵族,浸透着要靠工人的赞同和支持,而不靠强制来照顾工人阶级利益的责任感。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英国成为今天的样子更多地要归功于十九世纪保守党的原则,而不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思想。
无疑,影响罗斯福“新政”的另一样板是瑞典。瑞典走的是“中间道路”,这是马奎斯·蔡尔德1936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瑞典于1915年颁布了强制性的养老金法,该制度的资金来自人们的捐助。规定给予所有年过六十七岁的人以养老金,不论其经济状况如何。养老金的数目依个人向该制度捐款多少而定。该制度也得到政府的财政补助。
除养老金和后来的失业保险外,瑞典还大规模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兴建公共住房以及建立消费者合作社。
福利国家的结局
长期以来被标榜为福利国家的成功典型的英国和瑞典,遇到了愈来愈多的困难,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英国感到越来越难以承担日益增加的财政负担。税收成了不满情绪的主要根源。通货膨胀更给人们的不满情绪火上加油(见第九章)。一度成为福利国家桂冠上的明珠而且至今仍被多数英国公众视为工党政府的伟绩之一的国民保健事业,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境,受到罢工、费用上涨和病人等候时间延长等问题的困扰。越来越多的人转而依靠私人开业医生、私人健康保险、私人医院和私人疗养所。尽管私人成份在整个健康事业中仍占很小部分,但这部分却正在迅速增长。
英国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一起增长。政府不得不收回它实现充分就业的许愿。最糟糕的是,英国的生产率和实际收入再好也只能算是停滞不前,这使它大大落后于欧洲大陆上的邻邦。保守党在1979年选举中大获全胜是这种不满情绪的集中体现。这一胜利是由于玛格丽特·撒切尔保证彻底改变政府的政策而获得的。
瑞典的情况比英国好得多。它在两次大战中都没有负担,从中立地位中的确得到了好处。尽管如此,它近来也经历了与英国同样的困难: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高额所得税使一些最有才能的人移居国外;人们对社会纲领普遍不满。在这里,选民也以投票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意见。1976年,选民们结束了社会民主党四十多年的统治,代之以其他政党的联合执政。然而,政府的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在美国,纽约市是企图依靠政府规划来做好事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纽约是美国最注重福利的城市。按人口计算,纽约市政府的开支比美国其他任何城市都大,为芝加哥的两倍。我们可以从纽约市长罗伯特·瓦格纳1965年的预算演说中看到指导该市活动的基本原则,他说:“我不主张让财政问题来限制我们应对满足市民的基本需要承担的义务。”瓦格纳及其继任者对市民的“基本需要”作了非常广义的解释。但是,更多的金钱、更多的福利计划、更多的税收都无济干事。它们导致了财政上的灾难,不要说瓦格纳讲的广泛需要,就连起码的“人民的基本需要”也未能满足,只是靠了联邦政府和纽约州的资助才免于破产。这种资助的代价是纽约市交出了控制自己事物的权力,受到了州和联邦政府的严密监护。
纽约市民自然要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归咎于外界势力的影响。但是,正如肯·奥雷塔在新近的一本书中写道的,纽约“并非出于被迫,搞那规模巨大的医院和市立大学体系,也没有谁迫使它实行免费教育,无限制地招生,忽视预算的限制,征收国内最高的赋税,胡乱借款,向中等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严格控制房租,给城市工人以优厚的养老金、工资和其他小恩小惠。”
他讽刺道,“受自由主义的热忱和财富再分配的理想主义信念的驱使,纽约的官员们帮助把许多税款和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分配给了纽约以外的地方。”
值得庆幸的是,纽约市不具有发行钞票的权力。它不能利用通货膨胀作为征税的手段,这才延迟了灾祸的到来。可惜,它并不正视自己的问题,只是向纽约州和联邦政府求救。
让我们更加仔细地看看以下几个例子。
社会保险
美国在联邦一级的主要福利国家项目是社会保险。它包括对老年、遗属、残废和健康的保险。正如巴里·戈德华特在1964年发现的,一方面,它是一头任何政治家都不敢碰的圣牛;另一方面,它又是众矢之的。领取津贴的人抱怨说靠补助金维持不了应有的生活水平。为社会保险纳税的人们则抱怨负担太重。雇主们抱怨说,在雇主多雇一名工人所花的钱和这个就业工人所得的净收入之间插进这些税造成了失业。纳税人抱怨说,这个未备基金的社会保险系统的负担总额已达数百亿美元,即便是目前的高税率也不能维持很久。这一切抱怨都有其道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实行社会保险和失业保险,是为了使工人能够为自已准备退休金或暂时失业时的补贴,而不必依靠救济。政府只是补贴那些真正贫穷的人,而且本来打算随着就业情况的好转和社会保险事业的普遍开展,逐步取消政府救济。这两个计划开始时规模都很小,但后来却盲目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目前看不出社会保险有取代政府救济的迹象。在耗资和领取补助的人数方面,二者都空前巨大。1978年为退休、残废、失业、医疗保健和遗属抚恤支付的社会保险金总共超过一千三百亿美元,领取者超过四千万。四百多亿美元的政府救济发给了一千七百多万人。
为把讨论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这一节的探讨将仅限于社会保险的主要部分,即对老年人和遗属的补贴上。他们得到的津贴几乎占整个福利开支的三分之二,人数占领取福利金总人数的四分之三。下一节再讨论政府救济计划。
社会保险法于本世纪三十年代通过,自那时以来,社会保险事业便贴着假标签,通过骗人的广告宣传,被到处推销。如果是一家私营企业进行这种骗人的宣传活动,无疑会遭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斥责。
一直到1977年,在一本题为《大众社会保险》的未署名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发行了上百万份的小册子上,年复一年刊载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社会保险的基本思想很简单:就是在就业期间,雇主、雇员和自雇人员支付社会保险金,用这些钱设立特殊的信托基金。当工人由于退休、残废或死亡而没有收入或减少了收入时,将按月给予一定的、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家庭收入的减少。”
以下是奥韦尔(译注:奥韦尔是美国社会党人布莱尔的笔名,下文《一九八四年》一书的作者。)的矛盾观念。
工资税被称为“捐款”(或象该党在《一九八四年》那本书中说的,“强制即自愿”)。
在人们的想象中,信托基金似乎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它们的数目向来很少(1978年6月,老年和遗属保险基金为三百二十亿美元,按当时的支出情况,不足半年之用),而且,只是政府的一个机构答应向另一机构付款。当前按社会保险法已经答应给退休或尚未退休的人的养老金的总值,已达数万亿美元。要证明小册子的话正确,就需要这样数目的信托基金(用奥韦尔的话说,“少即多”)。
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工人的“福利”是靠自己的“捐款”来支付的。实际上,支付给退休工人、退休工人家属和工人遗属的福利金,是从就业工人那里征收的税款。根本就没有设立真正的信托基金(“我即你”)。
今天纳税的工人从信托基金那里得不到保证,他们退休时将得到福利。任何保证都取决于未来的纳税人,要看他们是否愿意为现在的纳税人许诺给自己的津贴纳税。这种单方面的“隔代契约”被强加给一代代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同意。这与“信托基金”是两码事,倒不如说更象一封连锁信。
现在发行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小册子还说:“在美国,每十名就业者中有九名为自己和家庭挣得社会保险计划的保障。”
更为矛盾的是:现在每十名就业者中,有九名在为非就业者的津贴纳税。向私人养老金机构捐款的人可以说是在为自己“挣取”保障。而向政府机构纳税的人则不能说是在为自己和家庭“挣取”保障。他只是在政治意义上“挣取”保障,即满足政府的一定要求以取得享受福利的资格。现在接受补助的人们所得到的,要比他们自己缴纳的税和别人为他们缴纳的税的总值高得多。而许诺给现在缴纳社会保险税的年青人的,要比他们将要缴纳的税和别人将为他们缴纳的税的总额少得多。
社会保险并不是一种交多少钱就能拿到多少津贴的保险计划。甚至它的最坚决的支持者也承认,“个人所捐的钱(即工资税)与他所得到的津贴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社会保险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税和一种特殊的转移开支计划的混合体。
有意思的是,我们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个人,不论其政治倾向如何,会替税收制度或福利制度本身辩护。如果把这两种制度分开来考虑,哪种制度也不会被人们采纳。
至于福利方面的赋税,虽然最近作了一些小改小革(即根据收入情况给予回扣),但仍然是对所有等级的工资按统一比率征税。因而这是一种累退税,低收入者负担最重,是对工作征收的税,使雇主不想雇用工人,人们不想找工作。
至于津贴的安排,它既不由领取者所付的钱数来决定,也不由他的收入情况来决定,既不能公平地偿还原先所付的钱,也不能有效地帮助贫困者。在所付的税款和所得到的津贴之间虽然也有某种联系,然而它最多不过是一块遮羞布,以使人们能大言不惭地把这种结合叫做“保险”。一个人能够得到多少津贴完全取决于各种偶然因素。如果他恰好在保了险的行业工作,他可得到津贴;如果他恰好在一个没有保险的行业工作,他就得不到津贴。如果他在一个保了险的行业中干的时间不长,不管他多么贫困,也是什么也得不到。而一位从不工作的妇女,如果她是一位可以享受最高津贴的人的妻子或未亡人的话,那她得到的津贴会和一位同她情况相同的劳动妇女除工资外得到的津贴相等。一位年过六十五岁的人,如果决定去干活,而且每年挣得中等以上的收入,那他不仅得不到津贴,更倒霉的是,还要额外纳税——想来是为了补偿那没有支付的津贴。这种事例举不胜举。
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保险计划是“新政”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该计划把一种人们不能接受的赋税和一种人们不能接受的补贴方法结合在一起。我们很难想象有哪个异想天开的计划能比这个计划取得更大的成功。
纵观社会保险方面的各种文章和书籍,我们对那些用来为该计划辩护的论证感到震惊。一些不会对自己的孩子、朋友或同事撒谎的人,一些在日常的私人交往中最让人信得过的人,竟然会在社会保险这一问题上宣传错误的观点。他们的才智和对相反观点的揭露,使人难以相信他们在进行这种宣传时,是出于无意和无知。他们显然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精华,最知道什么对别人有益,认为有责任和义务去说服选民为那些会对他们有益的法律投票,为此,即使欺骗他们也在所不惜。
长期以来,社会保险计划的财政困难是由一个简单的事实造成的: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数,比可以为福利津贴纳税的人数增长得快,而且今后还将更快。1950年,每一个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有十七个人为其纳税;到1970年只剩下了三人为其纳税;如果目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到二十一世纪初,最多将只有两人为其纳税。
上述情况表明,社会保险计划把收入从青年人那里转移给了老年人。从整个历史来看,这种转移在某种程度上早已存在了,以往青年人总是供养他们的父母或其他上了年纪的亲属。的确,在许多象印度那样有着很高死婴率的贫穷国家。养儿防老是造成高出生率和大家庭的主要原因。社会保险和早先供养父母的习惯的区别在于,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非个人的事情,而供养父母则是自己愿意的个人私事。道义的责任是个人而不是社会的事情。孩子照顾自己的父母是出于爱或责任感。现在,他们为供养别人的父母解囊是由于受到政府的强制和出于恐惧。早先的那种转移加强家庭的纽带,而强制的转移则削弱这种纽带。
【按:美国以前也是祖孙三代同堂的社会,直到社会保障制度的扩大。】
除了从青年人向老年人的这种转移,社会保险还包括从不那么富裕者向比较富裕者的转移。福利津贴的发放确实是偏于照顾工资较低的人。然而,这种照顾被另外一种情况大大地抵消了。穷人家的子弟开始工作因而开始纳税的年龄都比较早;而富人家的子弟则晚得多。另一方面,就生命周期而言,低收入者的寿命平均比高收入者的寿命短。结果,穷人纳税的年头比富人长,领取福利津贴的年头比富人短,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穷人。
社会保险的其他一些特征更加强了这种反常的效果。福利津贴领取者的其他收入越高,从所得税中扣除的福利额就越大。对于年龄在六十五至七十二岁(1982年将改为七十岁)之间的老人,发给的津贴数额完全取决于他在那些年的工资收入,而不看其他方面的收入——有一百万美元的股息收入也不妨碍领取社会保险津贴;而年薪超过四千五百美元的人,却要为他所得的每两美元收入损失一美元的津贴。
总而言之,社会保险是“董事法规”在起作用的极好范例,即“公共开支是为了中等阶级的基本福利,而作为公共开支来源的赋税则主要由穷人和富人来负担。”
政府补助
讨论“一团糟的福利”可以比讨论社会保险简单得多,因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看法比较一致。我们现行的福利制度的弊病已被广泛地认识到了。尽管富裕程度在增长,但领取救济金的人数也在增加。庞大的官僚机构主要忙于来往公文的处理,而不是真正为人民干事。人们一旦靠上救济,就很难脱离救济金而生活。国家日益分化为两类公民,一类人领取救济,另一类人为救济出钱。那些领取救济的人就不想再挣钱了。救济金在国内各个不同的地方差异很大,这鼓励了人们从南方和农村地区向北方特别是城市中心移居。尽管经济情况可能相同,但是,正在接受救济或受到过救济的人与没有受过救济的人(即所谓穷工人)却往往受到政府的不同对待。贪污腐化和欺诈行贿,以及大事报导的福利“皇后”驾着用多种救济券买来的高级轿车到处周游的新闻,一次又一次地激起公众的愤怒。
【按:对比国内的红十字会,美国情况还算好点的。】
在对福利计划的抱怨增加的同时,受埋怨的福利计划的数目却在不断增加。已经通过的帮助穷人的联邦计划,乌七八糟地有一百多个。其中主要的计划有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对老年人的医疗照顾、对穷人的医疗补助、对有子女家庭的补助、保险收入补助、食品券;还有大多数人未听说过的无数小计划,如对古巴难民的援助、对妇女、婴儿和儿童的营养补助、对婴儿的特别照顾方案、房租补助、城市灭鼠方案、综合治疗血友病中心等等。许多计划是重叠的,有些设法得到多项福利补助的家庭,其最后的收入肯定要比全国平均收入还高。而另一些家庭或则由于行动得慢了些,或则由于不太关心这种事,往往申请不到补助来减轻他们真正的贫困。然而,每项计划都需要有官僚机构去管理。
社会保险每年耗资一千三百多亿美元,除此之外每年还要在这些福利计划上开支大约九百亿美元(十倍于1960年的开支)。这显然是太多了。1978年的所谓贫困线是:一个非农业的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在七千美元以下。据人口普查估计,当时大约有两千五百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中。这是个粗略的过高的估计,因为它仅仅根据工资收入来划线,全然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收入,如房产、花园、食品券、医疗补助、公共住房。有些研究报告认为,算上这些收入的话,“人口普查”的数字可以减少一半或四分之三。但是,即使根据人口普查的估计数字来计算,福利计划的开支分给每个贫困线以下的人,也合三千五百美元左右,分给每个四口之家合一万四千美元左右。约为贫困线水平的两倍。如果这些福利资金确实都花在“穷人”身上,就不会还有穷人,至少他们也可以舒服地过富裕的生活了。
显然,大部分福利开支没有用在穷人身上。其中有些被行政开支挪用,以优厚的薪金维持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有些到了那些绝不能被认为是穷人的手中。这些人中间有领取食品券或其他补助的大学生,有收入相当不错而又领取住房补贴和其他各种我们想象不到的补贴的家庭。还有些则到了骗取福利金的人手中。
我们有必要在这些福利计划上多费些口舌。同领取社会保险津贴的人们不同,靠这一巨额福利款项补助的人们的平均收入,可能比为补助他们而纳税的人们的低,不过即使这一点也很难确定。正如马丁·安德森所说:
“我们的福利计划可能效率很低,弊病很多,管理质量很差。有些计划彼此重叠,福利金的分配很不公平,而且没有能够在物质上刺激人们去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倒退一步,按照以下两个基本标准来考查各色各样的福利计划,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两个标准是:福利计划服务的对象之广泛和人们得到的服务之全面。按这两个标准衡量,我们的福利制度是辉煌的成就。”
住房补助
政府提供住房的计划在“新政”年代初始之时规模不大,后来迅速扩大。1965年新设立了一个部,即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该部现有近两万名雇员,每年开支一百亿美元以上。联邦住房计划得到各州和市政府计划的补充,特别是在纽约州和纽约市得到了大力补充。开始实行该计划时,政府只是为低收入家庭建造住房。战后,又增添了城市复兴计划。许多地区扩大了住房计划,向“中等收入的”家庭也提供公共住房。最近,又增加了“房租补贴”计划,政府为租赁私人住房提供房租补贴。
按最初的目标来看,这些计划显然是失败了。遭到破坏的住房,比建造起来的住房要多。住在享有房租补贴的公寓里的家庭,得到了好处。而那些由于自己的住房毁坏,无处栖身而被迫迁入更差的住宅的人家,住房情况则有所恶化。今天美国的住房和分配情况胜于公共住房计划开始实行之日,然而,这全赖私人企业之力,跟政府补贴没有多大关系。
公共住房常常沦为贫民窟和犯罪特别是青少年犯罪的温床。最明显的例子是圣路易斯的普鲁特·艾戈公共住房工程。该工程是一个占地五十三英亩的巨大的公寓群。其设计曾荣获建筑奖。然而,它已损坏得如此严重,以至不得不炸掉它的一部分。那时节,它的两千个单元中只有六百个住了人。人们说,它看上去象是个发生过巷战的地方。
1968年游历洛杉矶市瓦茨区时遇到的一件事,我们至今记忆犹新。陪同我们参观的是一位管理完善的自助工程的负责人。该工程是由工会倡议的。当我们赞扬这一地区的一些公寓时,他气愤地打断了我们的话,说:“瓦茨区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正是那些公共住宅。”他接着又说:“你怎么能指望那些住在完全由破裂家庭组成的开发区里、几乎完全靠福利救济为生的年轻人,养成良好的品德呢?”他还慨叹开发区对少年犯罪和附近学校产生的不良影响。那些学校的孩子很多都来自破裂的家庭。 最近,我们从纽约南布朗克斯的一个叫做“血汗资本”住房工程的领导人那里听到了类似的议论。该地区看上去象是被轰炸过的城市。许多建筑由于房租控制而被抛弃,另一些则毁于暴乱。“血汗资本”团体同政府商定,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复那些被废弃的住房,修好后,所有权归私人所有。开始时,他们从外界只得到少数私人捐款的支援,最近,也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些帮助。
当我们问他人们为什么不直接搬进公共住宅而费这么大的力气去修复旧房时,他作了我们在洛杉矶听到的同样的回答,不过又添了一句说,建造并拥有自己的住宅会使参加这一工程的人具有一种自豪感,这会使他们精心维修住宅。
“血汗资本”团体得到的政府援助,一部分是工人的劳务。这些工人根据综合就业训练法由政府支付工资,被派到各种不同的公共工程去接受训练,以便获得技能后能在私人企业中就业。当我们问他,“血汗资本”团体是愿意让综合就业训练法雇用的工人来帮忙,还是宁愿得到支付给工人的钱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宁愿得到钱。总之,人们在这种自助工程上表现的自力更生精神和干劲与他们在公共住宅工程上表现的那种明显的冷漠、无谓和厌倦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看到这些是令人鼓舞的。
纽约市实施的据说可以防止“中等收入家庭”逃离城市的住房补贴计划,情景大不一样。宽敞豪华的公寓以补贴的方式租给那些只有在极宽裕的意义上才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的家庭。对每套公寓的补贴平均每月在二百美元以上。“董事法规”又在起作用。
城市复兴计划旨在消灭贫民窟——“城市枯萎病”。对于需要重建的地段,政府出钱征用和清除,清理了的地皮大多以人为的低价供私人开发者利用。城市复兴计划“要拆迁四座住宅,才能建造一座住宅,拆迁的大都是黑人居住的房屋,而建造好的房屋大都供中等或上等收入的白人家庭居住。”原先的住户被迫迁移到其他地方,常常又使新的地段害“枯萎病”。某些批评者把城市复兴计划称为“贫民窟迁移计划”和“黑人迁移计划”,倒是名副其实的。
公共住宅和城市复兴计划的主要受益者并不是穷人,而是某些房地产主(他们的财产被政府征购来建造公共住房或者其财产正好位于要重建的地段)、中等和上等收入的家庭(它们能在高价公寓中或者在那些常是靠拆除低租房子重新盖起的市内公寓中找到住房)、市区商业中心的开发者和占有者以及能够利用城市复兴计划改善自己附近环境的大学和教会等公共机构。
正如《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篇社论指出的那样:
“联邦贸易委员会考察了政府的住宅政策,发现这些政策并非完全出于利他主义的目的。该委员会的一份政策简报发现,联邦住房政策的主要推动者似乎是那些靠盖房发财的人,如承包商、银行家、工会、建筑材料商等。一旦住宅建成后,政府和上述各色各样的‘赞助人’就对它不那么感兴趣了。因此,联邦贸易委员会常常听到人们抱怨住宅的质量,指责根据联邦计划建造的房子屋顶漏水,管道不足和地基不牢等等。”
另外,由于政府实行房租管制等措施,即使不是由于故意毁坏,一些低价出租的住宅也因无人修缮而日益破旧。
医疗照顾
医药是政府在最近一个时期扩大其作用的一块福利阵地。在公共卫生(环境卫生、传染 病等)以及提供医院设施方面,州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发挥作用,联邦政府也在较小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另外,联邦政府还为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提供医疗照顾。但直至1960年,政府用在人民保健事业方面(即不包括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的开支仍然不到五十亿美元,只占国民收入的1%强。自1965年实施医疗照顾方案和医疗补助方案后,政府在保健事业方面的开支迅速增加,1977年达到六百八十亿美元,约占国民收入的4.5%。政府在全国医疗总开支中所占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从1960年的25%增加到1977年的42%。然而,要求政府起更大作用的呼声仍然越来越大。卡特总统已对实施国民健康保险计划表示赞同,但限于财力,只能以有限的方式来搞。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没有这种顾虑,他主张立即通过法律由政府对全国公民的保健负完全责任。政府在医疗上的额外开支与私人健康保险的开支齐头并进。从1965年到1977年,医疗费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长了一倍。医疗设施也增加了,但费用没有增加得那么快。其必然结果是医药费和医生以及其它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员的收入猛增。
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曾试图管理医疗服务并压低医生和医院的收费。这是它应当做的事。政府既然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自当关心花了钱得到了多少好处:这叫作出资者做主。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其最终结果不可避免地会是医疗社会化。
【按:这里的医疗社会化其实是政府所有化,和国内说法不同。】
国民健康保险是使人产生误解的另一个例子。国民健康保险不同于私人保险:在你所交的钱与你可能得到的福利总额之间没有联系。另外,国民健康保险并不是为了给“国民的健康”(一个毫无意义的词)保险,而是为本国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它的倡议者所提倡的实际上是社会化的医疗制度。著名的瑞典医学教授、瑞典一家大医院的内科主任根纳·俾奥克博士曾写道:
“几千年来的行医过程是病人作为医生的顾客和雇主。今天,国家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自命为雇主,要由它来规定医生工作的框框。这些框框可能不会——最后一定不会——限于工作小时、薪金和药品的规格;它们可能影响病人和医生的所有关系。……如果今天不打这一仗并取得胜利,明天就没有仗可打了。”
美国提倡医疗社会化的人们,为了使其事业名正言顺,过去总是引用英国,最近总是引用加拿大的例子作为成功的样板。加拿大最近才实行医疗社会化,还不能对它下结论,因为新扫帚总是扫得特别干净,但它现在已经出现了困难。美国的国家卫生局已经建立了三十多年,对其作用我们现在完全可以下一结论了。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被举出来代替英国作为样板的原因。英国医生马克斯·甘蒙博士用了五年时间研究国家卫生局。他在1976年12月提出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国家卫生局)实际上使全国所有医疗服务都由中央政府提供资金,由中央政府进行控制。在过去二百年中发展起来的民间医疗事业几乎已完全被消灭。现行的强制性医疗制度经过改组实际上已成为普遍的医疗制度。”
另外,“在国家卫生局建立的最初十三年中,实际上没有新建一座医院,而现在,1976年,英国拥有的医院床位比在1948年7月刚建立国家卫生局时还要少。”而且,这些床位中的三分之二是设置在1900年以前由私人医生和私人资金建立起来的医院里的。
甘蒙博士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他所谓的官僚取代论:即机构越官僚化,无用工作取代有用工作的程度也越大,这可以说是帕金森定理的一种有趣的延伸。他用英国1965至1973年医院服务的材料证明了这一理论。在这八年期间,医院的工作人员总数增加了28%,行政和协助办事人员增加了51%,但按每日床位的平均使用率来计算的产量却下降了11%。而且正如甘蒙博士赶忙补充的,这并非是由于缺少病人使用的床位。在任何时候,都总有六十万左右的人等待医院的床位。许多被保健机构认为是可收可不收或可以等些时候的病人,要等几年才能得到手术治疗。
【按:英剧《是大臣》第二季第一集中的圣爱德华医院勉强算只有一名病人,却有五百名办事人员。编剧对社会的很多方面了解很是深刻。】
医生纷纷逃离英国。每年移居国外的医生约相当于英国医学院校毕业生人数的三分之一。近来,私人行医、私人健康保险、私人医院和私人疗养所迅速增加,也是对国家保健事业不满的结果。
在美国,实行医疗社会化的论据主要有两个:一,大多数美国人负担不起医药费;二,医疗社会化将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医药费用。第二个论据可以立即排除;至少是在有人能找到一个政府管理比私人经营更为经济的事例以前。至于第一个论据,可以说人民总是要这样或那样支付医药费用的,问题只在于,是人民直接自行支付这些钱,还是通过政府官僚来支付。这些官僚们会从中抽去相当大的一部分作为他们自己的薪金和开支。
无论如何,大多数美国家庭支付得起普通医药费用。他们可以进行私人保险,以应付意外的特大开支。住院费用的90%已经由第三者偿付。人们有时肯定会遇到特殊困难,这时应该由私人或政府提供某种帮助。但偶尔帮助人们克服困难,并不能证明强加给全国人民一套制度是合理的。
我们可以从以下的比较感觉到医疗费用的巨大:私人和政府花在医疗事业上的费用,总共为住房建设费用的三分之二,汽车制造业开支的四分之三,烟酒制造业开支的两倍半。烟酒业的开支无疑增加了医疗费用。
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实行医疗社会化。相反,政府在医疗方面的作用已经太大了。它的作用的任何进一步扩大将违反病人、医生和保健人员的利益。在第八章“谁保护工人”中,我们将讨论医疗的另一方面,即发放医生执照和这一措施对美国医学会的权力的影响。
福利国家的谬论
为什么这些计划都如此令人失望呢,它们的目标肯定是人道的和崇高的。但为什么没有成功呢。
新纪元初始之时,一切看来都好。要救济的人很少。能资助他们的纳税人很多——这样每人只需支付不大的数目,就可以为少数穷人提供可观的救济金。随着福利计划的扩大,这些数字发生了变化。今天,我们大家都从一个口袋里掏出钱,又把它(或它可以买得的东西)装进另一只口袋里。 把开支作一简单的分类,就能够说明为什么这一过程会导致不良的结果。当你花钱时,可能花的是你自己的钱,也可能是别人的钱,你可能是为自己花,也可能是为别人花。把这两对可能性编在一起,可以得出以下简图中归纳的四种可能性:
你是花钱者
| 谁的钱\为谁花 | 你 | 别人 |
|---|---|---|
| 你的 | I | II |
| 别人的 | III | IV |
Ⅰ类指的是你为自己花自己的钱,如你到超级市场买东西。你显然有强烈的愿望,既要省钱,又要使所花的每一美元都花得尽可能合算。
Ⅱ类指的是你为别人花你的钱,如你买耶诞节或生日礼物。你会象Ⅰ类中那样希望省钱,但并不同样想要花得最上算,至少根据接受人的爱好来判断是如此。当然,你要买接受者喜爱的东西,只要它能产生好的印象而又不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假如你的主要目的是让接受者能获得尽量多的价值,你会送给他现金,将Ⅱ类中由你花钱变为Ⅰ类中由他花钱)。
Ⅲ类指的是你为你自己花别人的钱。例如,可报销的用餐。你没有强烈的愿望要少花些钱。但你会有强烈的愿望想使钱花得上算。
Ⅳ类指的是你为另一个人花别人的钱。例如,你用报销单替另一个人付饭费。在这种情况下,你既不会想省钱,也不会想让客人吃得最为满意。然而,如果你同他一起用餐的话,那么,这顿饭就成了Ⅲ类和Ⅳ类的混合体,你就会有强烈的愿望满足你自己的口味,必要时可以牺牲他的口味。
所有福利计划不是属于Ⅲ类——如社会保险,福利金领取者可以按自己的愿望随便花他领到的钱——就是属于Ⅳ类——如公共住房;只是在Ⅳ类中带有一点Ⅲ类的特征,即管理福利计划的官僚们分享这顿午餐;而在Ⅲ类的所有计划中都有官僚们夹在福利金领取者中间。
我们认为,福利开支的这些特点是其缺点的主要根源。
立法者投票表决时是决定如何花别人的钱。选出立法者的选民在某种意义上是投票决定这是一个很好的表述方式,是我们和电视节目的到制片人埃本·威尔逊共同讨论产生的。
【按:政策可以设定为谁支持谁出钱。】
如何为自己花自己的钱,但不是在Ⅰ类那种直接花费的意义上。在个人缴纳的税款与他投票赞成的花费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实际上,选民同立法者一样,倾向于认为是别人在支付由立法者直接投票赞成、由选民间接投票赞成的计划。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僚们也花别人的钱。因此,开支数目激增也就不足为奇了。
官僚们为别人的需要花别人的钱。只有用良心,而不是用那强烈得多和可靠得多的私利的刺激,来保证他们以最有利于福利金领取者的方式花钱。这就造成花钱上的浪费和不求效果。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拿别人钱的引诱力是强烈的。包括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僚们在内,许多人都设法为自己得到钱,而不让钱落到别人手里。进行贪污和欺诈的诱惑力也是强烈的,而且并不总是能遭到反抗或制止。那些不愿进行欺骗的人,会用合法的手段使钱归于自己。他们会运动议员通过于他们有利的立法,定出他们能从中获利的规章。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员们会力求为他们自己得到更高的薪水和额外的好处——这正是较大的福利计划可以帮助达到的目标。
人们试图把政府开支归入自己的腰包,产生了两个不大容易被人查觉的后果。首先,它说明了为什么如此多的计划施惠于中等和上等收入者,而不是那些本应当得到好处的穷人。穷人变得不仅缺少市场上所看重的本事,而且缺少在政治斗争中成功地争得资金的本事。的确,他们在政治市场上的劣势看来比在经济市场上的劣势更大。一旦好心的改革者帮助通过了一项福利措施,转入下一项改革时,穷人就只好自己照料自己,他们几乎总是被那些已经表明更善于见机行事的集团所压倒。
第二个后果是,福利金领取者得到的净额,往往少于转移金的总额。如果有别人的一百美元可以攫取,那么为得到它你花上自己的一百美元也值得。花钱运动立法者和制定规章的当局,为政治运动和无数其他事项捐款纯属浪费——既损害出钱的纳税者,又无益于任何人。必须把它们从转移总额中除去,才得到净所得——当然,它们常常超过转移总额,结果剩下的不是净所得,而是净损失。
争取补贴的这种结果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有人要施加压力来增加开支和福利计划。最初的措施未能达到提倡它们的好心的改革者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就得出结论认为做得还不够。并谋求增添福利计划。他们同那些希望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僚们,以及相信能从福利开支中捞到油水的人们结成了同盟。
Ⅳ类开支还容易腐化接触到它们的人们。所有福利计划都使一些人处于决定什么对别人有利的地位。结果是,一部分人感到自己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另一些人则感到自己象孩子那样需要别人照顾。被救济者的独立自主的能力由于弃而不用而萎缩了。除了金钱的浪费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外,其最终结果是腐蚀了维持一个健全社会所必需的道德结构。
Ⅲ类或Ⅳ类开支的另一副产品具有同样的效果。除了人家白给你的钱外,如果你要花别人的钱,就只有象政府那样把别人的钱拿到自己手里。因此,福利国家到头来总是要使用强力,这一有害的方法往往使良好的愿望落空。这也是为什么福利国极其严重地威胁我们的自由的原因。
怎么办
大多数现行的福利计划,当初根本不应该制定。如果没有制定这些计划的话,许多现在依赖福利金的人很可能会成为自食其力的人,而不是受政府保护的人。这样做,对某些人来说一时可能显得不近人情,因为这使他们不得不干报酬低微而乏味的工作。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却是非常人道的。不过,福利计划既然已经实施,就不是一夜间能够一扫而光的了。我们需要某种方法使我们从目前所处的状况顺利地过渡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状况,为现在依赖福利金的人提供援助,同时鼓励人们从领福利金有条不紊地转到领工资。
这样一个过渡纲领可以增强个人责任感,结束目前把人们划分为两个阶段的状况,缩小政府开支和现在庞大的官僚机构,同时保障国内每个人的安全,到那时谁也不会再受贫困的煎熬。不幸的是,眼下要通过这样一个纲领似乎只是乌托邦的幻想。挡道的既得利益集团太多了,有思想上的、政治上的、财政上的,等等,许多许多。
尽管如此,看来仍值得向人们介绍这样一个纲领的主要内容。当然,我们并不指望它会在最近的将来被采纳,我们只想指明应该努力的方向,从而促进事态向这个方向发展。
这个纲领有两项基本内容:第一,改革现在的福利制度,用一个单一的内容广泛的现金收入补贴计划(这是一种与正所得税相联系的负所得税)取代目前杂七杂八的单项计划;第二,在履行现有义务的同时,逐步取消社会保险,要求人们自己为退休后的生活作出安排。
这种广泛的改革,将使我们目前实行的既不人道、又无效率的福利制度变为比较人道、比较有效的制度。它将向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确有保证的最低限度的补助,而不问他们需要的原因。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尽可能少的损害他们的名誉、独立性或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主动性。
一旦我们透过那掩盖正所得税的本质特征的烟幕,负所得税的基本概念就简单易懂了。根据现行的正所得税制度,允许你有一定数目不必纳税的收入。其确切数额,视你家庭人数的多少、你的年龄和你是否列举清楚你的扣除额而定。这个数额由以下几部分构成:个人豁免额、低收入免税额以及标准扣除额(最近它被重新定名为零级数额),总额相当于一般赋税优惠额。另外,据我们所知,还有偷税漏税的能手加进的许多数额,他们很会在缴纳个人所得税上玩一些鬼把戏。为便于讨论,让我们用“个人免税额”这个较为简明的英国术语来称呼这个基本数额吧。
如果你的收入超过免税额,超过的部分得按累进的税率纳税。如果你的收入低于免税额呢,在现行制度下,那免税额一般是无价值的。你只是无需纳税而已。
如果接连两年你每年的收入恰好与免税额相等,那么,在这任何一年中你都无需纳税。假设你这两年加起来的收入还是这么多,但有一半多是头一年得到,那你就有正数值的应纳税收入,也就是说你第一年的收入超过了免税额,因而必须纳税。而到第二年,你则有负数值的应纳税收入,也就是说免税额超过了收入。但一般来讲,你从免税额上得不到什么好处。最后这两年加在一起,你将比这笔收入均分在两年中缴纳更多的税款。
有了负所得税,你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未用上的免税额的一部分作为补贴。如果你得到的这一部分与正收入的税率相同,那么,无论你的收入在这两年中如何划分,你所缴纳的税款总额总是相等的。
当你的收入高于免税额时,你就要纳税,税额视收入额的多少而定。当你的收入低于免税额时,你会得到补贴,其数额根据未用上的免税额的多少而定。
正如我们所举的例子所表明的,负所得税将考虑到收入的波动,但这并不是它的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毋宁说是要提供一种简便的方法,确保每个家庭有一份最低的收入,同时避免庞大的官僚机构,使人们具有很强的个人责任感,打心里想去工作,想挣大钱来纳税而不是领补贴。
请看下面这个具体数字的例子。1978年,一个四口之家(其成员无人超过六十五岁)的免税额是七千二百美元。假定当时有所谓负所得税,其补贴率为未用上的免税额的 50% ,那么一个无收入的四口之家就有资格获得三千六百美元的补贴。如果这个家庭有人找到了工作,有了收入,补贴将被削减,但是,这个家庭得到的总收入(补贴加挣得的收入)将增加。如果收入为一千美元,补贴将减少到三千一百美元,而总收入上升为四千一百美元。实际上,所挣的收入一半用来弥补减少的补贴,一半用来增加总收入。一旦家庭所挣收入达到七千二百美元,补贴就降为零。七千二百美元是平衡点。在这个点上的家庭,既得不到补贴,也用不着纳税。如果家庭所挣收入继续增加,它就要开始纳税了。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研究行政管理的细节——补贴是按一星期,按两星期,还是按月支付,怎样检查执行情况,等等。所要说的只是:对这些问题都已作过彻底的研究,并拟有详细的计划,提交给了国会(这件事我们以后还要提到)。
负所得税制如能取代我们现有的许多专门的福利计划,我们现在的整个福利制度将会得到令人满意的改革。如果它只是变成整个福利垃圾堆里的又一件破烂,那就弊多利少了。
如果负所得税制果真取代了各种福利计划,那将带来巨大的好处。该制度是专门用来对付贫困问题的。它将以最实用的形式,即用现金来资助接受者。它是综合性的,而不是因为接受者年纪大,有疾残,患病,或生活在某一地区,也不是因为任何其他使人们在现行福利制度下可以得到救济金的原因。它给予资助,是因为接受者收入低。它明白地规定由纳税人承担费用。象任何其他设法减少贫困的措施一样,它也会减少促使人们自助的刺激。但是,只要把补贴率限定在合理的水平上,它就不会完全消除这种刺激。因为多挣一块美元,总是意味着有更多的钱可花。
同样重要的是,负所得税制可以免除目前管理这一大堆福利计划的庞大官僚机构。负所得税可以直接成为现行所得税制的一部分,并且可以一起管理。由于每个人都要填报所得税单,它可以减少现行所得税制度下的逃税漏税现象。可能要增添一些人员,但增添的人决不会多于目前管理福利计划的人。
通过取消庞大的官僚机构,使补贴制与税收制相互结合,负所得税可以铲除目前的不正常现象,即一些人——掌管福利计划的官僚们——操纵着他人的生计。它将有助于消除当前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级的状况:纳税阶级和依靠政府救济过活的阶级。只要平衡点和税率定得合理,负所得税制将比我们现行的制度省钱得多。
对于某些由于这样或那样原因无能力料理自己事务的家庭,给予个人帮助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由负所得税来维持穷人家庭的收入,这种帮助可以,而且会由私人慈善活动来提供。我们认为,现行福利制度最大的代价之一在于,它不仅破坏家庭,而且减少私人慈善活动。
社会保险怎么能够实现这一在政治上总是行不通的美妙梦想呢?
依我们看,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实行负所得税制与逐步减少社会保险结合起来,同时继续履行现有的义务。其方法如下:
1.立即废除工资税。
2.按现行法律规定的数额,继续付给现在享受社会保险的人以应得的钱。
3.给予每个已经挣得保险的工人以享受退休、残废或遗属福利津贴的权利。这些福利金是工人根据现行的法律迄今已付的税款和所挣得的收入使他有权获得的,但要减去由于废除工资税而今后少缴纳的税款所折合的福利金数额。工人可以选择他所要的福利津贴的形式,可以是将来的一份年金,也可以是公债,其价值与按照目前规定他有权得到的福利津贴的价值相等。
4.给予每个尚未挣得保险的工人一笔钱(同样采取公债券的形式),数目等于他或他的雇主为他已缴纳的税款的累计价值。
5.停止积累保险津贴,让个人按自己的愿望为退休后安排养老。
6.从总的税收和政府发行的公债中为上述第2、3、4项开支提供资金。
这样一个过渡性纲领丝毫不会增加美国政府的实际债务。相反,它会由于不再向未来的福利津贴接受者许诺而减少债务。它只是把现在隐蔽的债务公开化。它为现在未备基金的计划提供资金。这些步骤会导致大多数现存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立即解散。
逐步减少社会保险,将消除目前社会保险制度给就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意味着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它将增加个人储蓄,从而导致更高的资本形成率和更快的收入增长率。它将刺激私人养老金计划的发展和扩大,从而使许多工人感到生活更有保障。
哪些是政治上可行的?
这的确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不幸的是,在目前根本没有实施的可能。尼克松、福特和卡特这三任总统都考虑或推荐过包含有负所得税成分的计划。但政治上的压力迫使他们提出的计划只是作为现行福利计划的补充,而不是取代它们。补贴率都定得如此之高,以致这个计划对福利津贴领取者挣钱起不了什么刺激作用。这种畸形的计划只会把整个福利制度搞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尽管是我们最先提出用负所得税制代替目前的福利制度,但我却在国会作证,反对尼克松总统根据负所得税的想法提出来的“家庭补助计划”。
一项可实施的负所得税制,在政治上往往遇到两种互相关联的障碍。较为明显的障碍来自现行福利计划的既得利益者:福利津贴领取者,认为自己可以受益于福利计划的州和地方政府官员,而首先是管理福利计划的官僚。不那么明显的障碍是,福利改革的鼓吹者,包括现有的既得利益者,所要达到的目标互相冲突。
关于福利问题,马丁·安德森著有一本书,其中写得非常好的一章是“不可能彻底改革福利制度”,在这一章中他写道:
“所有彻底的福利改革计划都由三个政治上极为敏感的基本部分组成。第一是改革后基本的福利水平,例如为一个四口之家提供多少福利津贴。第二是改革计划在刺激接受福利津贴的人寻找工作和挣更多的钱方面将起什么作用。第三是改革是否会给纳税者带来额外的负担。
……改革计划要成为政治现实,必须在改革后仍然为现在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提供象样的补助,必须能强烈地刺激人们工作,而且给纳税者带来的负担必须是合理的。这三者必须同时兼顾。”
争论的焦点是怎样才算“象样”、“强烈”和“合理”,特别是怎样才算“象样”。如果“象样的”补贴意味着:现在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没有谁将因为改革而比当前少领津贴,那么,无论“强烈”和“合理”作何解释,也不可能同时达到上述三个目标。然而,正如安德森所说:“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国会决不会通过任何实际上会减少数百万福利津贴领取者所得的改革措施。”
让我们来看前一节中介绍的简单的负所得税制:一个四口之家的免征点是七千二百美元,按50%的补贴率计,凡没有收入来源的家庭可以得到三千六百美元的补助。50%的补贴率将给人以足够强烈的刺激去工作,而花费要比目前繁杂的福利计划省得多。但是,这种补贴标准今天在政治上是无法接受的。正如安德森所说:“现在(1978年初),美国典型的享受福利津贴的四口之家,每年可以得到大约六千美元的劳务和现金。在象纽约这样花销更大的州里,有些享受福利津贴的家庭每年得到的津贴在七千至一万二千美元之间,有的甚至更多。”
如果免征点定在七千二百美元,即便是收入六千美元的“典型”家庭,也需要有83.3%的补贴率。这样高的补贴率会严重地挫伤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同时大大增加开支。补贴率可以通过提高免征点来压低,但那又会极大地增加开支。这是一种无法解脱的恶性循环。要缩减从名目繁多的福利计划中得到高额福利津贴的人们的所得,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正如安德森所说:“我们不可能同时创造出进行彻底的福利改革所必需的全部政治条件。”
但是,今天政治上行不通,明天则可能行得通。在预言什么将成为政治上可行的事情上,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成绩非常糟。他们的预言一再被事实所否定。
我们的受人尊敬的伟大导师弗兰克·H·奈特喜欢用大雁由一只带头按人字形排队飞行的例子来说明不同的领导方式。他常说,当头雁一个劲儿地向前飞时,后面的大雁可能会飞向其他方向。头雁回头发现没有大雁跟随时,会赶紧掉头,重新带领人字形队伍朝前飞。这是一种领导方式。无疑,美国政府就常常采用这种方式。
我们承认,我们的建议目前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充分地说明我们的设想,不仅因为它是可以指导我们逐步进行改革的方针,而且还因为我们希望它终将成为在政治上可以办得到的事情。
结论
直到最近仍由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统治的王国,每年为我们的健康正在花费越来越多的钱。其主要结果只是增加医疗和保健费用,而医疗质量却没有任何相应的改进。教育经费也一直在激增,但教育质量却普遍地认为在下降。费用的上涨和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使我们不得不推行种族合校,而我们的社会看来却更为分崩离析。我们每年在福利事业上耗资数十亿美元。然而,在美国国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高的时候,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数却有增无减。社会保险的预算大得惊人,但社会保险却在财政上陷于严重的困境。年轻人颇有道理地抱怨,为接济老年人而要他们付的税太高。而老年人也颇有道理地抱怨,说他们无法维持被许诺的生活水平。制定的计划是要保证老年人不再成为救济对象,而看到的现实却是靠福利津贴生活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根据卫生、教育和福利部自己的计算,该部每年由于贪污受贿和铺张浪费损失的资金,足可以建造十万栋以上每栋耗资五万美元的住宅。
浪费是令人痛心的,但这不过是膨胀到这样大的家长式福利计划的祸害中最轻的一个。福利计划的主要祸害是对我们社会结构的影响。它们削弱家庭,降低人们对工作、储蓄和革新的兴趣,减少资本的积累,限制我们的自由。这些才是应当用来衡量福利计划的基本标准。
本节内容概述
从整个历史来看,这种转移在某种程度上早已存在了,以往青年人总是供养他们的父母或其他上了年纪的亲属。的确,在许多象印度那样有着很高死婴率的贫穷国家。养儿防老是造成高出生率和大家庭的主要原因。社会保险和早先供养父母的习惯的区别在于,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非个人的事情,而供养父母则是自己愿意的个人私事。道义的责任是个人而不是社会的事情。孩子照顾自己的父母是出于爱或责任感。现在,他们为供养别人的父母解囊是由于受到政府的强制和出于恐惧。早先的那种转移加强家庭的纽带,而强制的转移则削弱这种纽带。
如果负所得税制果真取代了各种福利计划,那将带来巨大的好处。该制度是专门用来对付贫困问题的。它将以最实用的形式,即用现金来资助接受者。它是综合性的,而不是因为接受者年纪大,有疾残,患病,或生活在某一地区,也不是因为任何其他使人们在现行福利制度下可以得到救济金的原因。它给予资助,是因为接受者收入低。它明白地规定由纳税人承担费用。象任何其他设法减少贫困的措施一样,它也会减少促使人们自助的刺激。但是,只要把补贴率限定在合理的水平上,它就不会完全消除这种刺激。因为多挣一块美元,总是意味着有更多的钱可花。
同样重要的是,负所得税制可以免除目前管理这一大堆福利计划的庞大官僚机构。负所得税可以直接成为现行所得税制的一部分,并且可以一起管理。由于每个人都要填报所得税单,它可以减少现行所得税制度下的逃税漏税现象。可能要增添一些人员,但增添的人决不会多于目前管理福利计划的人。
通过取消庞大的官僚机构,使补贴制与税收制相互结合,负所得税可以铲除目前的不正常现象,即一些人——掌管福利计划的官僚们——操纵着他人的生计。它将有助于消除当前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级的状况:纳税阶级和依靠政府救济过活的阶级。只要平衡点和税率定得合理,负所得税制将比我们现行的制度省钱得多。对于某些由于这样或那样原因无能力料理自己事务的家庭,给予个人帮助仍然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由负所得税来维持穷人家庭的收入,这种帮助可以,而且会由私人慈善活动来提供。我们认为,现行福利制度最大的代价之一在于,它不仅破坏家庭,而且减少私人慈善活动。
社会保险怎么能够实现这一在政治上总是行不通的美妙梦想呢?
依我们看,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实行负所得税制与逐步减少社会保险结合起来,同时继续履行现有的义务。其方法如下:
1.立即废除工资税。
2.按现行法律规定的数额,继续付给现在享受社会保险的人以应得的钱。
3.给予每个已经挣得保险的工人以享受退休、残废或遗属福利津贴的权利。这些福利金是工人根据现行的法律迄今已付的税款和所挣得的收入使他有权获得的,但要减去由于废除工资税而今后少缴纳的税款所折合的福利金数额。工人可以选择他所要的福利津贴的形式,可以是将来的一份年金,也可以是公债,其价值与按照目前规定他有权得到的福利津贴的价值相等。
4.给予每个尚未挣得保险的工人一笔钱(同样采取公债券的形式),数目等于他或他的雇主为他已缴纳的税款的累计价值。
5.停止积累保险津贴,让个人按自己的愿望为退休后安排养老。
6.从总的税收和政府发行的公债中为上述第2、3、4项开支提供资金。这样一个过渡性纲领丝毫不会增加美国政府的实际债务。相反,它会由于不再向未来的福利津贴接受者许诺而减少债务。它只是把现在隐蔽的债务公开化。它为现在未备基金的计划提供资金。这些步骤会导致大多数现存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立即解散。逐步减少社会保险,将消除目前社会保险制度给就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意味着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它将增加个人储蓄,从而导致更高的资本形成率和更快的收入增长率。它将刺激私人养老金计划的发展和扩大,从而使许多工人感到生活更有保障。
浪费是令人痛心的,但这不过是膨胀到这样大的家长式福利计划的祸害中最轻的一个。福利计划的主要祸害是对我们社会结构的影响。它们削弱家庭,降低人们对工作、储蓄和革新的兴趣,减少资本的积累,限制我们的自由。这些才是应当用来衡量福利计划的基本标准。
附录UBI和负所得税
弗里德曼提倡UBI是为了方便取消庞大的福利保障体系,我们这种负福利地区用不上这种方式。
附录【吴钩】《官办救济的困境》
作者:吴钩
来源:《华商报》2012-12-15
中国各代有各种官办的救济机构,初衷是为济贫救困、赈灾恤民,但权力的深度介入、官僚化的运作,日久都免不了弊病丛生,不但恤不了民,甚至成为“害民”之政。旧时常平仓、义仓与社仓的蜕变过程,给予后人一次又一次的教训。
常平仓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建制化官办公益机构(之一),汉代时已有常平仓之设置。所谓“常平”,乃是指“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以平抑物价。另外,常平仓也具有政府救济的功能,“如遇凶荒,即按数给散灾民贫户”。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罗斯福政府实行新政,还曾将常平仓思想引入美国农业立法。——按钱穆先生的说法,“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王安石)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担任过美国农业部长的华莱士也承认,“我接任农业部长后,在最快的时间内敦促国会通过立法,把中国古代农业政治家的实践——‘常平仓’引入美国农业立法中。”
从初衷看,常平仓不可谓不是“良法”。然而,历史的经验表明,任何官办机构几乎都免不了被权力异化,常平仓施行日久,也沦为“吏以为市,垄断渔利”之法。汉元帝时,诸儒提出毋与民争利,请罢常平仓。东汉明帝又拟设置常平仓,有官员即以常平仓“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为由,反对复置常平仓。从汉至清,常平仓的弊病几乎是定期发作的。
义仓出现的时间晚于常平仓,始见于隋朝:由官府“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之后唐太宗又将义仓之法加以完善、推广,规定“王公已下垦田,亩纳二升”,“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常平仓之粮出于官,而义仓之粮出于民,由政府强制征收,代为管理,类似于某种强制保险。
在官府力推之下,大唐“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谨,则开仓赈给”,义仓良法,看起来很美。然而,很快,义仓之粮便被官府挪作他用,“其后公私窘迫,渐贷义仓支用,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后世见识过社保基金被政府部门挪用来填补财政窟窿的人,对此应该不会感到意外。
义仓之败坏,其害甚于常平仓。原因宋人已说得很清楚了:“常平出于官,义仓出于民。出于官者,官自敛之,其弊虽不足以利民,亦不至于病民。出于民者,民实出之,官实敛之,其敛不但民无给,而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为常赋。”义仓之法,最后变成官府加税的名目,人民不但得不到救济,反而被强加了负担。
社仓是传统社会的NGO。第一个社仓由南宋士绅魏掞之1150年创立于福建招贤里。稍后(1168年),魏掞之的好友朱熹也在五夫里设立社仓。宋儒设置社仓的初衷,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的官方救济如常平仓不尽可靠,那么士绅就应当担起造福乡里之责,建立民间的自我救济体系,这样,乡人遇到凶岁饥荒时就不必全然依赖有司了。
社仓类似于今日社会贤达所办理的农村小额扶贫信贷,每年在青黄不接的五月份放贷,借米的人户则在收成后的冬季纳还本息。与青苗法不同,社仓由地方士绅组织并管理,人户是否要借贷也采取自愿原则,“如人户不愿请贷,亦不得妄有抑勒”。抑勒,就是强制、摊派之意。在朱熹的规划中,特别强调了社仓运作应独立于官方权力系统之外,不受官府干预。
1181年,朱熹上奏朝廷,建议在全国推行社仓之法。宋孝宗采纳了朱熹之议,下诏推广社仓,四五十年下来,朱子社仓“落落布天下”。然而,在社仓获得官府青睐的过程中,随着国家权力的介入越来越深,这一NGO组织也慢慢变质,最后居然成了“领以县官,主以案吏”的官办机构,并且跟青苗法一样暴露出“害民”的弊病,渐渐沦为害民之法,“非蠧于官吏,则蠧于豪家”。值得指出的是,“蠧于官吏”的危害无疑更甚于“蠧于豪家”,因为官吏掌握着“豪家”所没有的国家权力。时人俞文豹描述了南宋晚期社仓“蠧于官吏”的情形:一方面官府强制征收仓米,另一方面又将仓米挪作他用,即使遇到荒年,也“未尝给散”。民间公益给权力一插手,就变得乌烟瘴气了。
南宋末,朱熹的“再传弟子”黄震对官办的广德军社仓进行了“国退民进”的改革,“请照本法(朱子社仓之法)一切归之民”,即恢复社仓的NGO本色,委任地方士绅掌管仓米的借贷,官方只负责监督社仓“照官秤公平出贷”,而不准插手社仓的具体运作。黄震的社仓改革方向当然是对的。宋代社仓原本就是由士绅发起于民间、并且在士绅主持下运作良好的社会自组织,又何必要官府插上一脚?
社仓发展到清代时,又由于受政府控制,也出现了“蠧于官吏”的弊病:“近来官为经理,大半皆藉挪移,日久并不归款,设有存余,管理之首事与胥吏亦得从中盗卖”。到清代后期,由于社仓已荒废,不可修补,又有士绅出来“募捐田亩”,购置房屋设立义仓,“办理积仓备荒”。这里的“义仓”,为绅办,已不同于隋唐时期的官办义仓。这是义仓的再生。
现在,我们回头看看常平仓、义仓、社仓的兴衰轨迹,似乎可以得出一个道理:官办的公益救济,虽然从其初衷看,是“利民之良法”,但只要运行日久,几乎都无可避免地沦为“害民之恶法”。另一方面,面对官办机构的缺陷或败坏,儒家士君子也有足够的热情与技艺组织民间结社互助,主持NGO的良性运行。这才是中国传统社会得以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附录【吴钩】《宋王朝的国家福利与“福利病”》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赐稿
摘自 吴多纳新书《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
许多人可能都会以为,现代国家福利制度起源于1601年英国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这部法典将贫困人口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值得救济的穷人”,包括年老及丧失劳动力的残疾人、失去依靠的儿童,教区负有救济他们的责任,如给成年人提供救济金、衣物和工作,将贫穷儿童送到指定的人家寄养,待长到一定年龄时再送去当学徒工;另一类是“不值得被救济的人”,包括流浪汉、乞丐,他们将被关进监狱或送入教养院,接受强制劳动。
一些学者会告诉你,《伊丽莎白济贫法》的颁行,意味着英国“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社会救助制度”。这么言之凿凿的人,肯定不知道,也想象不到,比《伊丽莎白济贫法》更完备、更富人道主义精神的福利救济制度,实际上早在11~13世纪已经出现于宋代中国。
不相信吗?请跟着13世纪意大利的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到杭州看看南宋遗留下来的福利机构。马可·波罗在到达杭州之前,听说宋朝设有一种福利性的育婴机构:“诸州小民之不能养其婴儿者,产后即弃,国王尽收养之。记录各儿出生时之十二生肖以及日曜,旋在数处命人乳哺之。如有富人无子者,请求国王赐给孤儿,其数惟意所欲。诸儿长大成人,国王为之婚配,赐之俾其存活,由是每年所养男女有二万人。”
等到他来到杭州时,已经元朝了,杭州的育婴机构早已荒废多时。不过,他看到了另一种叫做“养济院”的福利机构:“日间若在街市见有残废穷苦不能工作之人,送至养济院中收容。此种养济院甚多,旧日国王所立,资产甚巨。其人疾愈以后,应使之有事可作。”
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有疑问:马可·波罗的记述可靠吗?
国家福利
我们不妨以宋朝人自己的记录为参证。吴自牧《梦粱录》载,“宋朝行都于杭,若军若民,生者死者,皆蒙雨露之恩”——
1)“民有疾病,州府置施药局于戒子桥西,委官监督,依方修制丸散【口父】咀,来者诊视,详其病源,给药医治,……或民以病状投局,则畀之药,必奏更生之效”;
2)“局侧有局名慈幼,官给钱典雇乳妇,养在局中,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无力抚养,抛弃于街坊,官收归局养之,月给钱米绢布,使其饱暖,养育成人,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
3)“老疾孤寡、贫乏不能自存及丐者等人,州县陈请于朝,即委钱塘、仁和县官,以病坊改作养济院,籍家姓名,每名官给钱米赡之”;
4)“更有两县置漏泽园一十二所,寺庵寄留槥椟无主者,或暴露遗骸,俱瘗其中,仍置屋以为春秋祭奠,听其亲属享祀,官府委德行僧二员主管”。
《梦粱录》所载者,是宋政府针对贫困人口而设立的四套福利系统:1)施药局为医药机构,代表医疗福利;2)慈幼局为福利孤儿院,代表儿童福利;3)养济院为福利养老院,代表养老福利;4)漏泽园为福利公墓,代表殡葬福利。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南宋时的杭州参观,走到戒子桥西,便可以看到施药局,旁边则是慈幼局,马可·波罗听闻的福利育婴机构,便是慈幼局。
这些福利机构并非仅仅设于都城杭州。北宋后期,朝廷已经要求“诸城、寨、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凡户口达到千户以上的城寨镇市,都必须设立居养院(即养济院)、安济坊、漏泽园,更别说人口更集中的州县城市了。南宋时,一些州县又创设了收养弃婴与孤儿的慈幼局,宝祐四年(1256),宋理宗下诏要求“天下诸州建慈幼局”,将慈幼机构推广至各州县。
宋理宗还说了一个心愿:“必使道路无啼饥之童。”至少在京畿一带,这位君主的理想已得以实现,因为一名元朝文人说:“宋京畿各郡门有慈幼局。盖以贫家子多,辄厌而不育,乃许其抱至局,书生年月日时,局设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无子女,许来局中取去为后。故遇岁侵,贫家子女多入慈幼局。是以道无抛弃之子女。若冬遇积雨雪,亦有赐钱例。虽小惠,然无甚贫者。此宋之所以厚养于民,而惠泽之周也。”这一记录,也可以证明马可·波罗所言不虚。
北宋时期虽然尚未出现专设的慈幼局,不过已有针对孤儿、弃婴的救济,宋徽宗曾诏令居养院同时收养孤儿:“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其衣襕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遗弃小儿,雇人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
南宋初,宋高宗又下诏推行“胎养助产令”:“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婴者,给钱养之。”给钱的标准是:“应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户,及无等第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于常平钱内,人支四贯文省”,符合救助条件的家庭,生育一名婴儿可获政府补助4贯“奶粉钱”。宋孝宗时又改为“每生一子,给常平米一硕、钱一贯,助其养育”。许多州县还设有地方性的“举子仓”,由地方政府向贫家产妇发放救济粮,一般标准是“遇民户生产,人给米一石”。
如果说,胎养令、举子仓与慈幼局代表了宋朝贫民“生有所育”的福利,养济院的出现则反映了宋人“老有所养”的福利。养济院是收养鳏寡、孤独、贫困老人的福利院,北宋时称为“居养院”,创建于元符元年(1098),这年宋哲宗下诏:“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崇宁五年(1106),宋徽宗赐名“居养院”,南宋时则多以“养济院”命名。
按宋人习惯,“六十为老”,年满60岁的老人,若属鳏寡、孤独、贫困,老无所依,居养院即有义务收养。宋徽宗时还一度将福利养老的年龄调低到50岁:“居养鳏寡孤独之人,其老者并年满五十岁以上,许行收养,诸路依此。”按北宋后期居养院的救济标准,“应居养人,日给粳米或粟米一升、钱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钱五文省”。
宋人还有“病有所医”的福利——体现为福利药局与福利医院的设置。熙宁变法期间,宋政府成立了营利性的合卖药所,宋徽宗将它改造成福利性的和剂局、惠民局,南宋相沿,行在临安与地方州县均设有官药局。官药局类似于现在的平价门诊部、平价大药房,如江东提刑司拨官本百万,开设药局,“制急于民用,……民有疾咸得赴局就医,切脉约药以归”;建康府的惠民药局,“四铺发药,应济军民,收本钱不取息”;临安府的施药局,“其药价比之时直损三之一,每岁糜户部缗钱数十万,朝廷举以偿之”,施药局诊病配药,药价只收市场价的三分之二,由户部发给补贴。有时候,施药局也向贫困人家开放义诊,并免费提供药物。
除了官药局,宋代还设有福利医院,即安济坊。安济坊配备有专门的医护人员,每年都要进行考核:“安济坊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疗痊失,岁终考会人数,以为殿最,仍立定赏罚条格。”病人在安济坊可获得免费的救治和伙食,并实行病人隔离制,以防止传染:“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又作厨舍,以为汤药饮食人宿舍。”
此外,宋朝的一些地方政府还设立了安乐庐,这是针对流动人口的免费救治机构。如南宋时,建康府人口流动频繁,常常有旅人“有病于道途,既无家可归,客店又不停者,无医无药,倾于非命,极为可念”,政府便设立安乐庐,凡“行旅在途”之人,发现身有疾病后均可向安乐庐求医,“全活者不胜计”。
人生的起点是摇篮,人生的归宿是坟墓,最后我们还要看看宋朝在“死有所葬”方面的福利。历朝官府都有设义冢助葬贫民、流民的善政,但制度化的福利公墓建设要到北宋后期才出现,宋徽宗要求各州县都要建造福利公墓,取名“漏泽园”:“凡寺观旅梓二十年无亲属、及死人之不知姓名、及乞丐或遗骸暴露者,令州县命僧主之,择高原不毛之土收葬,名漏泽园”。蔡京政府对漏泽园的建设尤为得力。
漏泽园有一套非常注重逝者尊严的制度:“应葬者,人给地八尺、方砖二口,以元寄所在及月日、姓名若其子娉、父母、兄弟、今葬字号、年月日,悉镌讫砖上,立峰记识如上法。无棺柩者,官给。已葬而子娉亲属识认,今乞改葬者,官为开葬,验籍给付。军民贫乏,亲属愿葬漏泽园者,听指占葬地,给地九尺。无故若放牧,悉不得入。仍于中量置屋,以为祭奠之所,听亲属享祭追荐。”
根据这段记载,可以知道,漏泽园的坟墓有统一规格,约八尺见方,以两块大方砖铭刻逝者的姓名、籍贯、生辰、安葬日期,有亲属信息的,也刻于砖上,作为标记。没有棺木的逝者,政府给予棺木收殓;已在漏泽园安葬者,如果有亲属愿意迁葬他处,政府将给予方便;贫困家庭的亲人去世后想安葬于漏泽园的,政府也允许——当然,不用收费。漏泽园设有房屋,以便逝者的亲属来此祭祀。
总而言之,对于贫困人口,宋朝政府试图给予“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关怀,提供的基本福利涵盖了对“生老病死”的救济。宋徽宗曾毫不谦虚地说:“鳏寡孤独,古之穷民,生者养之,病者药之,死者葬之,惠亦厚矣。”宋代福利之发达,不管跟后来的元明清时期相比,还是与近代化刚刚开始时的欧洲国家相较,都堪称领先一步。
过度福利
更有意思的是,宋朝“济贫政策所引发的关注及批评,已有类似近代国家福利政策之处”。近代国家常见的从福利政策衍生出来的“福利病”,同样存在于宋朝。请注意,我们要说的宋朝“福利病”,是指国家福利制度的衍生问题,而不是管理不善或制度漏洞所导致的弊病。
正如我们在一些福利国家所看到的情形,宋朝政府的福利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也诱发了“过度福利”的问题。宋徽宗的诏书一再指出过这个问题。
大观三年(1109)四月,宋徽宗在一份手诏上说:“居养、安济、漏泽,为仁政先,欲鳏寡孤独养生送死各不失所而已。闻诸县奉行太过,甚者至于许供张,备酒馔,不无苛扰。”有些州县的福利机构为救济对象提供酒馔,待遇不可谓不优厚。皇帝要求有司纠正这股“过度福利”之风:“立法禁止,无令过有姑息。”
次年,即大观四年八月,徽宗重申:“比年有司蹑望,殊失本指。至或置蚊帐,给肉食,许祭醮,功赠典,日用即广,縻费无艺。”诏令各州县停止福利扩张与靡费铺张,除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之外,不要自行设置其他的福利机构。
十年后,即宣和二年(1120)六月,宋徽宗再次下诏批评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资给过厚”的做法:“居养、安济、漏泽之法,本以施惠困穷。有司不明先帝之法,奉行失当,如给衣被器用,专雇乳母及女使之类,皆资给过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居养院与安济坊不但免费提供一切日常用具,还替接受救济的人雇请了乳母、保姆与陪护,以致政府的财政拨款入不敷出。
《嘉泰会稽志》也记载说,“居养院最侈,至有为屋三十间者。初,遇寒惟给纸衣及薪,久之,冬为火室给炭,夏为凉棚,什器饰以金漆,茵被悉用毡帛,妇人、小儿置女使及乳母。有司先给居养、安济等用度,而兵食顾在后。”
这种“縻费无艺”的“过度福利”,显然跟制度缺陷、监管不力造成的“福利腐败”并非同一回事。宋代的福利机构当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不过那是另一个话题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宋代“过度福利”,与其说是福利腐败,不如说跟政府的施政偏好密切相关。
宋朝福利的鼎盛期是蔡京执政的时期。为什么蔡京那么热衷于推行福利政策?因为他是新党领袖王安石的继承人,用现在的话语来说,北宋新党具有鲜明的左派风格,他们推动变法的目标之一便是“振乏绝,抑兼并”,希望运用国家的强制力与财政资源,救济贫困人口,抑制兼并,防止贫富分化悬殊。
蔡京拜相执政之年,宋徽宗将年号“建中靖国”改为“崇宁”,即意味着君臣宣告终止之前调和左右的折中政治,恢复熙宁变法的左翼路线。蔡京政府也确实以“振乏绝,抑兼并”为己任。蔡氏曾经告诉徽宗:“自开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贸易,富者恃其有余,厚立价以规利;贫者迫于不足,薄移税以速售,而天下之赋调不平久矣。”表达了对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的关切。后来蔡京下台,接任的宰相王黼“阳顺人心,悉反蔡京所为”,其中就包括“富户科抑一切蠲除之”,这反证了蔡京执政时实行过“科抑富户”的左翼政策。
也因此,蔡京一上台执政,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的建设便迅速在全国铺开,乃至出现“过度福利”。而当蔡京罢相时,宋朝的福利制度又会发生收缩,如大观四年、宣和二年,皇帝下诏纠正“过度福利”,都是蔡京罢相之时。
养懒汉
我们现在都说,优厚的福利制度下,很容易“养懒汉”。在蔡京执政之际、北宋福利制度迅速扩张的时期,确实出现了“养懒汉”的问题,比如一些州县的居养院和安济坊,由于政府提供的生活条件非常不错,“置蚊帐,给肉食”,甚至还有保姆、做家政的阿姨,所以便有“少且壮者,游惰无图,廪食自若,官弗之察,弊孰甚焉”,在居养院或安济坊中赖着不走,白吃白喝白睡。
许多到过西欧国家旅游的人都会发现,高福利制度已经深刻塑造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节奏:每天工作几小时,要么就成天晒太阳,经常休假旅游,大街上很少看到行色匆匆的上班族。这种图享乐、慢节奏的生活风气,也出现在南宋时的杭州社会。
如果马可·波罗在南宋时就来到杭州,他将会看到,西湖一带,“湖山游人,至暮不绝。大抵杭州胜景,全在西湖,他郡无此,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乐事之时,讵宜虚度?至如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终日游玩的人,不但有“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这等富贵子弟,还有“解质借兑”(类似于今日城市刚刚兴起的“贷款旅游”)的城市贫民,“不特富家巨室为然,虽贫乏之人,亦且对时行乐也”。
这些贫乏的市民为什么能够“对时行乐”,乃至敢于“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怕饿死么?不怕。因为南宋杭州市民享受到的福利非常丰厚。
请看周密《武林旧事》的记载:“都民素骄,非惟风俗所致,盖生长辇下,势使之然。若住屋则动蠲公私房赁,或终岁不偿一钚。诸务税息,亦多蠲放,有连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认。诸项窠名,恩赏则有‘黄榜钱’,雪降则有‘雪寒钱’,久雨久晴则又有‘赈恤钱米’,大家富室则又随时有所资给,大官拜命则有所谓‘抢节钱’,病者则有施药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则有慈幼局,贫而无依者则有养济院,死而无殓者则有漏泽园。民生何其幸欤。”
南宋杭州市民所享受到的政府福利(私人慈善不计在内)包括:减免赋税,经常蠲免房屋租金;遇上大节庆,政府会发“黄榜钱”,碰上大雪天,发“雪寒钱”,久雨久旱则发放“赈恤钱米”;贫困的病人可到施药局免费诊治取药,被遗弃的孤儿会被收养入慈幼局,贫而无依之人送入养济院养老,死而无殓者安葬在漏泽园。
——换成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福利制度下,即使身无分文,也是敢“贷款旅游”,带着老婆孩子玩个痛快的。对不?
贫者乐而富者扰
福利制度看起来很诱人,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羊毛最终出在羊身上,不是出在这群羊身上,便是出在那群羊身上。宋政府维持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福利机构运转的经费,有几个来源:左藏库,即国家财政拨款;内藏钱,皇室经费的资助;公田的租息收入;国营商业机构的收入,比如“僦舍钱”,即官营货栈的租金收入;常平仓的利息钱米。其中常平仓的息钱为大头。如果常平仓息钱不足用,通常就只能挪用其他用途的财政款项或者增加税收了。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述了崇宁年间各州县倾财政之力办理福利救济的情形:“崇宁间初兴学校,州郡建学,聚学粮,日不暇给。士人入辟雍,皆给券,一日不可缓,缓则谓之害学政,议罚不少贷。已而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谚曰:‘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盖军粮乏,民力穷,皆不问,若安济等有不及,则被罪也。”以蔡京政府的施政偏好,救济贫民的福利支出优先于军费开销。军粮缺乏,可以容忍;济贫不力,则会被问责。
这并非陆游的虚构,因为徽宗的诏书可以佐证。宣和二年六月十九日,皇帝诏曰: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救济过度,“常平所入,殆不能支。天下穷民饱食暖衣,犹有余峙;而使军旅之士稞食不继,或至逋逃四方,非所以为政之道”。难怪当时的民谚要讥笑蔡京政府“不养健儿,却养乞儿”。
这是占用财政拨款的情况。宋徽宗的诏书还提到因“过度福利”而导致民间税负加重的问题:大观三年四月二日,皇帝手诏:“闻诸县奉行(福利救济)太过,甚者至于许供张,备酒馔,不无苛扰。”这里的“苛扰”,便指政府增税,骚扰民间。《宋史·食货志》也称,蔡京时代的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糜费无艺,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率敛”也是增税的意思。由于宋代的赋税主要由富户承担,而福利机构的救济对象为贫民,所以便出现“贫者乐而富者扰”之讥。
洪迈《夷坚志》中有一则“优伶箴戏”的故事,辛辣讽刺了蔡京时代“贫者乐而富者扰”的福利制度。故事说,三名杂剧伶人在内廷表演滑稽戏时,饰演成儒生、道士与僧人,各自解说其教义。
儒生先说:“吾之所学,仁义礼智信,曰‘五常’。”然后采引经书,阐述“五常”之大义。道士接着说:“吾之所学,金木水火土,曰‘五行’。”亦引经据典,夸说教义。
轮到僧人说话,只见他双掌合十,说道:“你们两个,腐生常谈,不足听。吾之所学,生老病死苦,曰‘五化’。藏经渊奥,非汝等所得闻,当以现世佛菩萨法理之妙为汝陈之。不服,请问我。”
儒生与道人便问他:“何谓生?”僧人说:“(如今)内自太学辟雍,外至下州偏县,凡秀才读书,尽为三舍生。华屋美馔,月书季考;三岁大比,脱白挂绿,上可以为卿相。国家之于生也如此。”(这里的“生”,伶人理解为“书生”,指的是国家的教育福利,恰可弥补我们前述所未及之处。)
又问:“何谓老?”僧人说:“(昔者)老而孤独贫困,必沦沟壑。今所在立孤老院,养之终身。国家之于老也如此。”
又问:“何谓病?”僧人说:“(生民)不幸而有病,家贫不能拯疗,于是有安济坊,使之存处,差医付药,责以十全之效。其于病也如此。”
又问:“何谓死?”僧人说:“死者,人所不免,唯穷民无所归,则择空隙地为漏泽园;无以殓,则与之棺,使得葬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其于死也如此。”
最后问:“何谓苦?”僧人“瞑目不应”,神情很是悲苦。儒生与道人催促再三,僧人才“蹙额”答道:“只是百姓一般受无量苦。”
教坊杂剧伶人表演这出滑稽戏,是想告诉皇帝,政府为维持庞大的福利支出,变着法子加税,已经使老百姓“受无量苦”了。看演出的宋徽宗听后,“恻然长思”,倒也没有怪罪讥讽时政的伶人。
为什么是宋朝?
在宋朝济贫政策的推行过程中,特别是在蔡京政府的“福利扩张”时期,“福利病”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这一点无可讳言。不过,有一个道理我认为也需要指出来:“过度福利”好比是“营养过剩”,一个营养不良的人是不应该担心营养过剩的;如果因为担心营养过剩而不肯吃肉,那就是跟“因噎废食”差不多的愚蠢了。
宋人的态度比较务实——既不齿于蔡京的为人,也抨击过“资给过厚”的“过度福利”,但对蔡京政府推行的福利制度本身,却是很赞赏,朱熹说:崇宁、大观之间,“始诏州县立安济坊、居养院,以收恤疾病癃老之人,德至渥矣。”甚至有宋人相信,蔡京为六贼之首,独免诛戮,乃是因为他执政之时,“建居养、安济、漏泽,贫有养,病有医,死有葬,阴德及物所致”。可见宋人只是反感“过度福利”,并不拒绝福利制度。
而在宋朝之外的朝代,我们就很难见到关于“福利病”的记载了。这当然不是因为其他王朝的福利制度更加完善,而是因为,宋朝之外的王朝,政府并未积极介入对贫困人口的救济,没有建立完备的福利救济机构。
尽管《周礼》中载有“保息六政”: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管子》中亦记录有“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但这只是带有福利色彩的政策,没有证据显示当时已设立了专门的福利机构。
南北朝时,南齐出现了免费收治贫病之人的“六疾馆”,北魏建立了功能相似的病坊,南梁则设有收养孤老与孤儿的“孤独园”,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福利机构,但不管是“六疾馆”,还是“孤独园”,全国只有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用。而且,建“六疾馆”的南齐太子萧长懋,建“孤独园”的南梁皇帝萧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准确地说,他们是以佛教徒(而非国君)的身份修建福利机构的。政府并没有创设福利制度的自觉。
唐代从京师到一些地方都出现了“悲田养病坊”,负责收养贫病孤寡,有时也收留流浪乞丐,但悲田养病坊是从寺院中发展起来的,日常工作也由僧人主持,“悲田”二字即来自佛经,唐政府只是给予资助并参与监督,与其说它是国家福利机构,不如说是民间慈善组织。
宋朝之后的元明清三朝,国家福利也出现了明显的退缩。我们知道,宋代的贫民福利体系包括四个系统:1)以官药局和安济坊为代表的医疗福利;2)以胎养令和慈幼局为代表的生育福利;3)以居养院或养济院为代表的养老福利;4)以漏泽园为代表的殡葬福利。恰好囊括了对贫民“生老病死”的救济。
这四个福利系统,除了医药救济得到元政府的重视之外,其他福利机构在元朝都被废弃了;明朝的朱元璋虽然重建了惠民药局与养济院两套系统,但惠民药局在明中期之后基本上已经荒废,“养济院”则被用于控制人口流动,因为明政府规定:街上的流浪乞丐要送入养济院收容,候天气和暖,再遣送回原籍;清王朝只保留了养济院的设置,并且同样利用养济院系统控制流民,至于对弃婴、孤儿的救济,则被清廷视为是“妇女慈仁之类,非急务也”。
总而言之,宋朝政府建立的“从摇篮到坟墓”全覆盖的贫民福利体系,我们在其他王朝是找不到的。没有发达的福利体系,又哪来衍生的“福利病”?
那么,为什么只有宋王朝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贫民福利制度的建设?你可能会说,因为宋朝皇帝推崇儒家的“仁政”。但哪一个朝代的君主不是以“推行仁政”相标榜呢?为什么他们在实际行动上又提不起兴建福利机构的劲头?
我读过历史学者梁其姿的大著《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受其启发,想提出一点综合的解释。
宋代福利制度的建立,首先是近代化产生的压力催化出来的结果。研究者发现,在16世纪的欧洲,当社会经济结构从封建制度过渡至资本主义制度之际,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个后果:由于社会经济急剧变化,大量都市贫民被“制造”出来,成为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近代欧洲国家逐渐发展出来的福利政策,其实就是为了应对这一崭新的社会问题。英国政府制订“济贫法”之举,即始于近代化正在展开的16世纪下半叶,及至17世纪初,便诞生了完备的《伊丽莎白济贫法》。“济贫法”的出现,意味着英国政府开始负担起救济贫民的责任,在此之前,英国的济贫工作主要是由教会承担的。
中国则在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大变革,历史学家们相信,唐朝是“中世纪的黄昏”,宋朝则是“现代的拂晓时辰”,伴随着均田制的解体、贵族门阀的消亡、商品经济的兴起、人口流动的频繁、“不抑兼并”与“田制不立”政策的确立,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催生了大量的都市贫困人口,传统的由宗教团体负责的慈善救济已不足以应对都市贫困问题,政府需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提供更周全的救济。而“官方的长期济贫机构在宋亡后约三百多年间没有进一步发展,反而萎缩,这当然并不说明元明间的贫穷问题减轻了,而是这三百年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没有如宋代一样使都市贫穷成为突出的问题”。
其次,宋朝福利制度的建立也是“大政府”政策取向的结果。纵览历史,我们会发现,宋王朝有着显著的“大政府”性格,政府不但设置了大量的经济部门介入商业活动,开拓市场,对涌现出来的都市贫困问题,也是倾向于以国家力量积极解决,不仅建立了针对贫民“生老病死”问题的福利救济机构,而且在政府的施政过程中,还出现了接近现代意义的“贫困线”概念(之前的王朝是不存在一条一般性的“贫困线”的):田产20亩以下或者产业50贯以下的家庭,即为生活在贫困线下的“贫弱之家”、“贫下之民”。贫民可以享有一系列政策倾斜与政府救济,如免纳“免役钱”,免服保甲之役,获得“胎养助产”补助,借贷常平米钱免息,发生灾荒时优先得到救济,等等。
为什么宋朝建立的绝大多数福利机构都在元朝消失了?一个不容忽略的原因便是,“此后的中央政府不似宋代的积极”。特别是朱元璋缔造的明王朝,更是表现出鲜明的“小政府”性格,国家财政内敛,公权力消极无为,政府职能严重萎缩,晚明之时,当都市贫困再次成为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朝廷依然缺乏兴趣去规划建设一个完整的福利体系。梁其姿总结说:“在政治理念方面,明政权又缺乏宋代的创意。明政府并不曾制定一套长期性的、全国性的社会救济政策。”这个评价是精准的,不过我们还要补充一句:以明王朝的内敛型财政,即便朝廷有心,也无力发展宋朝式的福利制度。清承明制,清王朝差不多也是如此。
不过,从晚明开始,由地方士绅主导的民间慈善力量已发育成熟,“既然政府并不正视新富及贫穷所带来的社会焦虑,地方精英自然而然地接手处理这个问题”。这便是自晚明至晚清期间,善会、善堂等民间慈善组织勃兴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要等到16世纪下半叶,随着英国“济贫法”的出台,政府救济机构的建立,国家才承担起向贫民提供救济的义务,之后,英国的福利制度慢慢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显然离不开重商主义财政的支撑。而中国在宋朝之后,囿于“小政府”的惰性,福利制度建设非但裹足不前,且比宋朝退步了,此消彼长,到晚清时,便完全落后于英国。
游历海外的晚清学者王韬发现,英国政府所征之税,“田赋之外,商税为重。其所抽虽若繁琐,而每岁量出以为入,一切善堂经费以及桥梁道路,悉皆拨自官库,藉以养民而便民,故取诸民而民不怨,奉诸君而君无私焉。国中之鳏寡孤独、废疾老弱,无不有养。凡入一境,其地方官必来告曰,若者为何堂,若者为何院,其中一切供给无不周备。盲聋残缺者,亦能使之各事其事,罔有一夫之失所。呜呼!其待民可谓厚矣。”如此情景,仿佛就是中国宋朝。
宋朝的福利制度尽管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包括福利制度衍生的“福利病”、由于监管不力而产生的“福利腐败”,等等,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否则福利制度,一个没有基本福利“兜底”的社会,是不可能安宁的。两宋天灾频仍,据学者的研究,其发生灾害的“频度之密,盖与唐代相若,而其强度与广度则更有过之”。宋代的民变也此起彼伏,300余年出现400多起民变,不过都是小股民变,很快平息,如果宋朝没有这么一个覆盖面广泛的国家福利系统,恐怕民变早就一发不可收拾。要知道,两宋可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发生全国性民变的长命王朝,这里面,应有国家福利“兜底”之功。
南宋诗人楼钥写过一首讲述家史的长诗《次韵雷知院观音诗因叙家中铜像之详》,里面有一句是这么说的:“衰宗幸有此奇特,信知福利非唐捐。”用这一诗句形容宋朝的福利制度,也是很恰切的。
附录【吴钩】《台风“山竹”过后,我们来谈谈宋朝人怎样运用经济学赈灾》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八月初九日癸丑
耶稣2018年9月18日
今年特大台风“山竹”来临之时,我正好在家乡近海小城,目击台风呼啸而过。又看到网友留言:“期待吴老师写一期大宋朝时候的台风灾害及赈灾”。那就来说说宋朝的台风与赈灾吧。
十一至十三世纪的宋王朝,由于恰好横跨了两个气候温暖期,中间还夹着一个寒冷期,气候变化频繁,导致自然灾害的出现也更加密集,两宋三百余年,单就史有记录的水灾,便有600多次。宋朝史料记载的台风,也是触目惊心,看样子比“山竹”还要厉害。
太平兴国七年八月,琼州飓风,坏城门、州署、民舍殆尽。九月,太平军飓风拔木,坏廨宇、民舍千八十七区。十月,雷州飓风坏禀库、民舍七百区。九年八月,白州(博白)飓风,坏廨宇、民舍。
乾道二年八月,温州大风,海溢,漂民庐、盐场、龙朔寺,覆舟,溺死二万余人,江滨胔骼尚七千余。
乾道五年夏秋,温、台州凡三大风,水漂民庐,坏田稼,入畜溺死者甚众,黄岩县为甚,郡守王之望、陈岩肖不以闻,皆黜削。
淳熙三年八月,台州大风雨,至于壬午,海涛、溪流合激为大水,决江岸,坏民庐,溺死者甚众。
庆元元年六月,台州及属县大风雨,山洪、海涛并作,漂没田庐无算,死者蔽川,漂沉旬日。
由于天灾频仍,宋朝的荒政也很完备,中国第一部救荒专书《救荒活民书》,便诞生在南宋。
宋代比较有现代气息的赈灾模式,表现为市场逻辑的崛起,政府有意识地运用市场机制赈济灾民,这其中的佼佼者,当推北宋名臣范仲淹与赵抃。
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皇祐二年(1050年),两浙路发生灾荒,“吴中大饥,殍殣枕路”,当时范仲淹为杭州知州,兼负责浙西一带的赈灾。范仲淹除了给饥民“发粟”之外,见“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便“纵民竞渡”,鼓励民间多办些赛龙舟活动,鼓励居民出游观看比赛。他自己则每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又叫来杭州的“诸佛寺主首”,告诉他们:“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诸寺主首觉得有道理,于是大兴土木,雇佣了许多工人。杭州政府也大举兴建“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
范仲淹的做法很快引起监察系统的注意,浙西路的监司弹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这也说明当时的监察系统反应灵敏、运作正常,如果无人出来弹劾,那才不正常)。范仲淹坦然处之。朝廷派人一调查,发现范仲淹之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范公的举措,恰好暗合了凯恩斯的理论,即通过扩大投资与鼓励消费来拉动经济,从而惠及民生。当时杭州的“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这无数人,都因为范仲淹施行的“凯恩斯经济刺激政策”,而不致失业、沦为流民。那一年,“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沈括赞扬说,此皆“先生之美泽也”。
二十年后的熙宁八年(1075年),两浙路又有灾荒,“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诸州政府为平抑粮价,皆在“衢路立告赏,禁人增米价”。米价虽然控制住了,但市场上却没有多少米可以出售。当时在越州(今绍兴)任太守的赵抃,则反其道而行之,命人贴出公告,宣布政府不抑粮价,有多余粮食之人尽管“增价粜之”,想卖多少价钱就卖多少价钱。如此一来,各地米商见有利可图,纷纷运米前往越州,很快越州的商品粮供应充足,米价也跌了下来。
这则故事记录在明代冯梦龙编撰的《智囊全集》中。冯梦龙讲完故事后评论说:“大凡物多则贱,少则贵。不求贱而求多,(赵抃)真晓人也。”而对“禁人增米价”的政府行为,冯梦龙则讽刺道,“俗吏往往如此。”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赵抃比俗吏的高明之处,是他不迷信政府权力的“看得见的脚”(行政命令),而更相信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正好暗合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
当然,赵抃的赈灾方式能够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也应归功于宋代已经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商品粮市场网络。宋人叶适说,湖南“地之所产米最盛,而中家无储粮。臣尝细察其故矣。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惟意,无有碍隔。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大商则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舰而同营,展转贩粜,以规厚利。”《清明上河图》就画了多条停泊在汴河上的漕船,那都是从南方运粮前来京师的。这些漕船看起来不像是官船(因为不见官兵押运),而是私人船只,可见当时民间市场化的漕运是相当发达的。
二十五年前范仲淹在杭州赈灾时,已经巧妙地运用了“看不见的手”,当时杭州米价升至120文每斗,范仲淹贴出榜文,称以每斗180文收购粮食,“商贾闻之,晨夕争先,惟恐后,且虑后者继来。米既辐凑,价亦随减”。
值得指出的是,并非只有范赵二公有此智慧,而是越来越多的宋人都已发现了“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南宋人董煟在他的《救荒活民书》中便明明白白地提出“不抑价”的赈灾主张:“惟不抑价,非惟舟车辐凑,而上户亦恐后时,争先发廪,米价亦自低矣。”董煟曾经看到,有一些地方,“上司指挥不得妄増米价”,“本欲存恤细民”,却“不知四境之外米价差高”,牙侩暗暗增价收购本地之米,转往他州,导致荒情加剧。好事办出了坏事。
赵忭在越州赈灾,也使用过范仲淹的“凯恩斯政策”,“僦(雇佣)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不管是依靠自由市场的机制来置配赈灾的资源,还是利用凯恩斯手段刺激经济,这一右一左的政策,当时都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想来,不能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附录【李竞恒】《孟子思想与克服“时间偏好”》
作者:李竞恒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文史天地》2023年第3期
奥地利经济学派有一项“时间偏好”(Time preference)的理论,讲现在消费与将来消费的边际替代率,说简单点就是储蓄给将来,还是马上就消费。马上就消费,就是有更强的时间偏好,反之就是时间偏好更低,如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就曾经在内华达大学的课堂上提到同性恋有更高时间偏好,因为没有子嗣作为未来的储蓄。
实际上,人类文明的诞生本身就是克服时间偏好的产物,因为从人的天性来说,都倾向于马上享受得到的事物,而将其进行储蓄留给未来,则需要克服本性,克服那种根深蒂固“爽一把就死”的原始本能。抓住一只小羊,忍住马上就将其吃掉的本能,而是把它养大,未来就能获得稳定的奶和羊毛,而农业和储存粮食更是训练了人克服时间偏好的能力,大量物质的储蓄也让一些人可以脱离农业劳动,产生了复杂的社会分工,进而促进了文明的诞生。
实际上,农业的诞生有效促进了人类克服时间偏好的能力,因为在狩猎采集社会,人们会倾向于将猎物和果实快速食用,而不是用以储蓄。而农业社会,必须克服时间偏好,忍着饥饿也要守着田里的谷物,留下一些储蓄作为来年的种子。如果收成好,就会储蓄更多粮食,最终成为未来的财富。
财产权的稳定,可以有助于人们克服时间偏好,有了稳定财产,一切储蓄都是有意义的,能看到明天的希望,除了积累财产,还包括储蓄善行、为家人积累口碑,这些都是留给未来和子孙的宝贵财富,这样的社会必然有利于美德的培养。反之,在超强时间偏好的社会,因为无法保证有财产或信誉之类,人们会倾向于在短时间内骗一把、抢一把就跑,爽一把就死。很显然,有稳定的共同体、财产能得到保护的地区和人群,可以更好地克服时间偏好,积累美好的未来。而共同体瓦解、遍地原子散沙,或者多天灾人祸的地方,很难积累稳定财产,这些地区和人群就倾向于短时间的博弈,爽一把再说,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
一
《围城》里面有个著名的“葡萄论”,就是先挑最好的葡萄吃,还是把好葡萄留到最后吃。如果从教育小孩克服时间偏好的角度,我会非常鼓励教小孩要把好吃的留到最后再享用,而克服自己首先就吃最好葡萄的那种原始本能。在汉语中,“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饮鸩止渴”这些体现超高时间偏好行为的词语都属于贬义词,这也意味着中国民间主流文化传统还是以克服时间偏好为价值取向的。
汉代民间就有很多存钱罐“扑满”,刘歆《西京杂记》卷五描述说:“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就是说扑满是当时储存硬币的存钱罐,民间普遍习惯储蓄硬币,而不是钱到手就马上花掉,表明至少汉代开始中国民间就有储蓄未来、克服时间偏好的文化,这和汉儒对社会的重建是有关的。
《孟子·滕文公上》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非常清楚,民众的财产得到稳定的保护,成为“恒产”,他们才能拥有“恒心”,即成为克服时间偏好后的文明人。只有在财产得到保护的前提下,自己一切给未来的储蓄——无论是多生几个小孩有助于养老、多收获了几担谷子换成铜钱储蓄、或者在村里帮助别人收获了良好口碑,这些才对自己的未来是有利的。反之,孟子说如果财产得不到保护,民众就会产生超高的时间偏好,即“无恒产者无恒心”,反正无论我怎么积累钱,马上就被石壕吏们榨取走了,我做好事积累口碑,马上被骗子利用还沦为笑话和反面教材,既然如此,那还是做坏事划算,至少偷一把、骗一把搞到钱马上胡吃海喝到肚子里面最实在。所以孟子说,这种超高时间偏好的社会,即“无恒产”和“无恒心”的社会,一定是“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当然,孟子还提出了“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即华夏社会受过绅士教育的精英“士”,无论在任何情形下都要保持克服时间偏好的能力,对积累未来负责任,即使是没有稳定财富,也不能像普通民众一样随波逐流,去骗去偷,而是用尽一切条件和努力去重建社会,让人们重新获得稳定的财产——即孟子所说的“制民之产”,然后去积累和储蓄未来。
要克服时间偏好,稳定的小共同体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熟人社会作恶成本高,俗话讲“兔子不吃窝边草”就是描述这种小共同体内的作恶成本问题。无论是家庭、家族还是跨血缘的乡党、村社这些小共同体,都是世世代代一起生活和博弈的人,因此博弈的时间线非常长,人们会考虑很长远的未来关系等制约条件,因此会克服时间偏好,不会像很多流民陌生人社会那样去作恶,爽一把就跑。孟子主张“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即乡党、村社世代互助的小共同体,内部成员互相扶持一起积累未来。这种关系,不仅仅是村社成员之间,还包括村社的领主,也和治下的村民之间凝结成世代博弈的关系,因此不会像后世那种只当三年就拍屁股走人的流官一样,具有超强时间偏好,赶快搞个大的政治工程然后升官走人,至于留下什么烂摊子不关他的事。王夫之曾这样描述孟子推崇的“三代”时期画面:“名为卿大夫,实则今乡里之豪族而已。世居其土,世勤其畴,世修其陂池,世治其助耕之氓,故官不侵民,民不欺官。”(《读通鉴论》卷十九)王夫之提到这些领主和他们属下的民众之间,是世世代代互相打交道的关系,博弈时间线非常长,作恶成本高,因此领主不欺负属民,属民也不欺负领主,双方都克服了时间偏好,考虑更长远子孙的未来和子孙的关系。
傅斯年也观察到,古老封建时代的官民关系亲密。他说:“试看《国风》,那时人民对于那时公室的兴味何其密切。”(傅斯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自《史学方法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7页)因为双方都属于世代博弈和交道的共同体内,这和后世流官完全不同。在流官的时代,频繁爆发农民起义,因为流官只对朝廷负责,反正当几年官就走人,时间偏好极其强烈,赶快搞个大工程,升迁走人,至于当地以后怎么样,关本官啥事?但封建时代,领主和属民的关系是以动辄几百年来计算的,因此双方的博弈行为模式都是最大化克服时间偏好,会考虑得非常长远。
顾炎武就意识到地方官克服自己时间偏好的重要性,长治久安就是克服时间偏好,有世家的社会,考虑的时间线条就更长,这就是更低的时间偏好。因此他在《郡县论》中提出要让县令世袭的方案,如果县令做得好、不违法,就可以传给子孙,完全和当地人同生死共命运,那么县令的思考时间线就会大不一样,他会尽可能克服时间偏好,为这个县的长远未来,以及自己在这个县的长期名誉、口碑而努力,因为自己家族的未来已经和这个地方永久绑定在一起。所以,顾炎武“寓封建于郡县”的思路,就是鼓励在县一级地方培植扎根深、考虑未来更长远、时间偏好更低的一些世家治理。这恰恰是帮助中央集权郡县制时代,克服时间偏好和彻底掏空地方的一种手段,保护了各个县一级的自治与长远未来。在没有封建的时代,却能得到封建的好处,而避免封建的坏处。
如果理解到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孟子提出“世卿世禄”的思想了,所谓“仕者世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下》),古老封建时代的官职长期是由一些家族世代担任的,西周铜器铭文经常会有周王任命新一代官员“更乃祖司某事”,即继承家族的世代职业和手艺。由于会考虑家族世世代代职业的口碑,这些世官会特别讲究类似工匠精神的东西,如以史官为例,封建时代的史官特别讲究秉笔直书这种职业道德,很大程度上就是史官整个家族和这一职业道德的绑定。王安石在《答韶州张殿臣书》中说:“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当时很多史官如董狐或者齐国的北史氏、南史氏之类,都是不避刀斧,也要坚持秉笔直书的,这是封建时代世卿世禄制度下,一个时代职业家族的职业伦理,这种世卿会考虑整个家族长远的利益和口碑积累,克服时间偏好,他们考虑的家族博弈时间线,动辄是以几百年为单位的,很长远,哪怕暂时吃亏,家中有人因秉笔直书被杀,但长远看却进一步积累了家族的良好口碑,对于未来更加有利。所以,孟子主张的世卿世禄背后,也有克服时间偏好的这一面。
二
与这些稳定长远共同体形成对比的,就是流民散沙社会,陌生人之间博弈线条极短,因此往往具有超强时间偏好,倾向于爽一把就死。
东晋时期的成汉君主李寿,在咸康四年(338)就曾经有一次占卜,得到结论是可以当几年皇帝。他手下的罗恒、解思明等都劝他不要自称皇帝,而是称成都王、益州牧就行了,以诸侯身份向东晋称臣,就可以得到东晋的保护,从而长远地当诸侯,延续自己的家族。所谓“数年天子,孰与百世诸侯”,当几年皇帝,哪有当上百代诸侯好?但是李寿生自流民家族,有强烈的时间偏好,他竟然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是爽一把皇帝就行(《资治通鉴·晋纪十八》)。既然称皇帝,那就是摆明和东晋作对,后来成汉被桓温所灭,也是咎由自取。显然,李寿完全误读了孔子那句话,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是“道”如果可以实现,自己愿意死去(李竞恒:《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8页),而“道”的实现恰恰是遍地都是克服时间偏好的自治共同体,而不是超强时间偏好的流民散沙。与李寿相比,同是东晋南朝的琅琊王氏,就非常聪明,晋、宋、齐、梁、陈朝代不断变化,但琅琊王氏的地位却不变,以“百世诸侯”的身份延续了三百年的基业,而不是灿烂几年就灭亡。显然,贵族精神品质的士族,比流民更能克服自己的时间偏好。
到了宋代,随着中古时期贵族社会的瓦解,出现了更均质性和扁平的社会结构,在“齐民”之间身份更平等的同时,问题也随之出现,就是更平民化的家庭组织不像古代贵族家族那样,能更好地克服时间偏好。对此宋儒张载有一番论述:“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张载集·经学理窟》,中华书局,2019年,第259页)。张载认为,孟子推崇的世家、世臣是一个社会和国家的顶梁柱和凝结核,贵族世家的时间考虑范围非常长远,如周公动辄“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琅琊王导动辄卜得“淮水竭,王氏灭”,家族生命线与大自然河流的生命一样久远。如果和这些贵族世家动辄几百上千年的时间线相比,来自平民科考当官的家庭,时间偏好确实更强烈,只是倾向于考虑“三四十年之计”,哪怕当了一回宰相,也不过造一栋大豪宅,然后死掉,家产就被子女们分了,散沙化、原子化,如同一个美丽烟花,绚烂绽放瞬间,然后烟消云散,什么都留不下。
因此,张载主张平民精英模仿先秦贵族,建立宗法,通过宗法手段建立起模仿古代贵族家族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通过宗法手段获得长远的生命,尽量不散沙化,而是将散沙的核心小家庭团成宗族共同体。个体的生命有限,但宗法承载的生命河流共同体可以无限,这样就不会只是考虑“三四十年之计”,而是会动辄考虑几百年、上千年的未来,那么博弈的行为模式就一定会很稳健,不会轻易干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和不考虑长远未来和子孙的事。宋代范仲淹留下的范氏义庄,运转九百年,堪称平民社会模仿古代贵族世家最成功的例子之一,这种动辄九百年的世家一定会强有力地克服时间偏好,而如果遍地都是这样的世家,对于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附录【李竞恒】《孟子论克服时间偏好:稳定的共同体、恒产是文明的前提》
作者:李竞恒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南方周末》2022年6月30日
奥地利经济学派有一项“时间偏好”(Time preference)的理论,讲现在消费与将来消费的边际替代率,说简单点就是储蓄给将来,还是马上就消费。
实际上,人类文明的诞生本身就是克服时间偏好的产物。因为从人的天性来说,都倾向于马上享受得到的事物,而将其进行储蓄留给未来,则需要克服本性,克服那种根深蒂固“爽一把就死”的原始本能。抓住一只小羊,忍住马上就将其吃掉的本能,而是把它养大,未来就能获得稳定的奶和羊毛,而农业和储存粮食更是训练了人克服时间偏好的能力,大量物资的储蓄也让一些人可以脱离农业劳动,产生了复杂的社会分工,进而促进了文明的诞生。
财产权的稳定,可以有助于人们克服时间偏好,有了稳定财产,一切储蓄都是有意义的,除了积累财产,还包括储蓄善行、为家人积累口碑,这些都是留给未来和子孙的宝贵财富,这样的社会必然有利于美德。反之,在超强时间偏好的社会,因为无法保证有财产或信誉之类,人们会倾向于在短时间内骗一把、抢一把就跑、爽一把就死。
很显然,有稳定的共同体、财产能得到保护的地区和人群,可以更好地克服时间偏好,积累美好的未来。而共同体瓦解、遍地原子散沙,或者多天灾人祸的地方,很难积累稳定财产,这些地区和人群就倾向于短时间的博弈,爽一把再说,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围城》里面有个著名的“葡萄论”,就是先挑最好的葡萄吃,还是把好葡萄留到最后吃。
《孟子·滕文公上》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非常清楚,民众的财产得到稳定的保护,成为“恒产”,他们才能拥有“恒心”,即成为克服时间偏好后的文明人。只有在财产得到保护的前提下,自己一切给未来的储蓄——无论是多生几个小孩有助于养老、多收获了几担谷子换成铜钱储蓄,或者在村里帮助别人收获了良好口碑,这些才对自己的未来是有利的。
反之,孟子说如果财产得不到保护,民众就会产生超高的时间偏好,反正无论我怎么积累钱,马上就被石壕吏榨取走了,我做好事积累口碑,马上被骗子利用还沦为笑话和反面教材,既然如此,那还是做坏事划算,至少偷一把、骗一把搞到钱马上胡吃海喝到肚子里面最实在。所以孟子说,这种超高时间偏好的社会,一定是“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
当然,孟子还提出了“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即华夏社会受过绅士教育的精英“士”,无论在任何情形下都要保持克服时间偏好的能力,对积累未来负责任,即使是没有稳定财富,也不能像普通民众一样随波逐流,去骗去偷,而是用尽一切条件和努力去重建社会,让人们重新获得稳定的财产,即孟子所说的“制民之产”,然后去积累和储蓄未来。
要克服时间偏好,稳定的小共同体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熟人社会作恶成本高,俗话讲“兔子不吃窝边草”就是描述这种小共同体内的作恶成本问题。无论是家庭、家族还是跨血缘的乡党、村社这些小共同体,都是世世代代一起生活和博弈的人,因此博弈的时间线非常长,人们会考虑很长远的未来关系等制约条件,因此会克服时间偏好,不会像很多流民陌生人社会那样去作恶,爽一把就跑。孟子主张“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即乡党、村社世代互助的小共同体,内部成员互相扶持一起积累未来。这种关系,不仅仅是村社成员之间,还包括村社的领主,也和治下的村民之间凝结成世代博弈的关系。
王夫之曾这样描述孟子推崇的“三代”时期画面:“名为卿大夫,实则今乡里之豪族而已。世居其土,世勤其畴,世修其陂池,世治其助耕之氓,故官不侵民,民不欺官”(《读通鉴论》卷十九),王夫之提到,这些领主和他们属下的民众之间,是世世代代互相打交道的关系,博弈时间线非常长,作恶成本高,因此领主不欺负属民,属民也不欺负领主,双方都克服了时间偏好,考虑更长远子孙的未来和子孙的关系。
如果理解到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孟子提出“世卿世禄”的思想了,所谓“仕者世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古老封建时代的官职长期是由一些家族世代担任的,西周铜器铭文经常会有周王任命新一代官员“更乃祖司某事”,即继承家族的世代职业和手艺。由于会考虑家族世世代代职业的口碑,这些世官会特别讲究类似工匠精神的东西,如史官为例,封建时代的史官特别讲究秉笔直书这种职业道德,很大程度上就是史官整个家族和这一职业道德的绑定。王安石在《答韶州张殿臣书》中说“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当时很多史官如董狐,或者齐国的北史氏、南史氏之类,都是不避刀斧,也要坚持秉笔直书的,这是封建时代世卿世禄制度下,一个时代职业家族的职业伦理,这种世卿会考虑整个家族长远的利益和口碑积累,克服时间偏好,哪怕暂时吃亏,家中有人因秉笔直书被杀,但长远看却进一步积累了家族的良好口碑,对于未来更加有利。所以,孟子主张的世卿世禄背后,也有克服时间偏好的这一面。
(作者系大学教师、历史学者)
第5章 生而平等
“平等“”自由”——《独立宣言》中的这两个词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它们所表达的理想能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平等与自由是相互一致的,还是相互抵触的?
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早在《独立宣言》之前,就已对美国历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寻求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形成了知识界的舆论,导致了血腥的战争,造成了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的巨大改变。寻求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将继续是我们政治辩论的主要内容。它将象影响我们的过去一样,影响我们的未来。
在共和国建国伊始的年代,平等指的是在陡斯面前的平等;自由指的是决定个人命运的自由。《独立宣言》和奴隶制之间明显的冲突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南北战争最后解决了这场冲突。辩论于是转到另一个高度。平等越来越被解释为“机会均等”,即每个人应该凭自己的能力追求自己的目标,谁也不应受到专制障碍的阻挠。对于大多数美国公民来说这仍然是平等的主要含义。
无论是陡斯面前的平等还是机会均等,都同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不存在任何冲突。恰恰相反,平等和自由是同一个基本价值概念——即应该把每个人看作是目的本身——的两个方面。
最近几十年来,平等这个词在美国开始具有一种同上述两种解释很不相同的含义,即结果均等。每个人应享有同等水平的生活或收入,而且应该结束竞争。结果均等显然是与自由相抵触的。努力推进这种均等,是造成政府越来越大并使我们的自由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
陡斯面前的平等
当托马斯·杰斐逊在三十三岁上写下《人人生而平等》时,他和他的同时代的人们并没有就字面上的含义来理解这些词。他们并不认为“人”——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个人”——在身体特征、情绪反应、技艺和知识上是平等的。托马斯·杰斐逊本人就是出类拔萃的人。在二十六岁那年,他设计了坐落在蒙提塞洛(意大利语意为“小山”)的漂亮房子,亲自监督建造,据说还自己动手。在他的一生中,他曾经是发明家、学者、作家、政治家、弗吉尼亚州州长、美国总统、驻法国大使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人——总之,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普通的人。
杰斐逊和他的同时代的人们对平等的理解,可以从《独立宣言》的下一段话中看出:“造物主赋予人们以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耶和华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其自己的价值。他有不可转让的权利,任何人不能侵犯。他有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应简单地被当作达到他人目的的工具。“自由”是平等定义的一部分。并不与平等相冲突。
耶和华面前的平等——人身平等——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人不是个个一样的。他们的不同价值观、不同爱好、不同能力使他们想过很不相同的生活。人身平等要求尊重他们这样做的权利,而不是强迫他们接受他人的价值观或判断。杰斐逊毫不怀疑,某些人优于另一些人,也不怀疑杰出人物的存在。但这并不赋予他们统治别人的权利。
如果说杰出人物集团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那么,任何其他集团,即便在人口中占大多数,也不拥有这种权利。每个人应该是他自己的统治者,只要他不去干涉别人同样的权利。建立政府是为了保护这种权利,使其不受其它公民或外界的威胁,而不是让多数人毫无约束地统治其他人。
杰斐逊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他生前取得的三项成就:一、在他任州长时,弗吉尼亚州通过了宗教自由法(该法是旨在保护少数人不受多数人统治的“美国权利法案”的前身),二、起草《独立宣言》,三、创办弗吉尼亚大学。由杰斐逊的同时代人起草的美国宪法,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全国性政府,以保卫国家,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但同时要严格限制它的权力,以保护每一个公民和各州政府不受全国政府的支配。统治民主,是指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府活动,显然不是指政治上由多数人实行统治。
著名的法国政治哲学家和社会学家A.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对美国作了长期访问后,写了一本不朽的著作,名叫《美国的民主》。他在书中认为美国的突出特征是平等,而不是多数人统治。他写道:
“在美国,贵族政治因素从一开始就是微弱的。即使它们尚未被完全肃清,它们现在也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很难再对事态产生任何影响。相反,民主原则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以及各项法律的制定而得到极大的加强,该原则不仅压倒了其他一切原则,而且成了无所不能的灵丹妙药。在美国,没有哪个家族或公司能够发号施令。……
因而,美国社会展示了最为奇特的现象。那里的人们看上去在财富和智力上,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力量上,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或任何有文字可考的古人,都享有更大的平等。”
托克维尔对他的所见所闻大加赞美,但他并不是盲目的吹捧者,他担心民主搞得过火,会败坏人们的德行。他写道:“有……一种大丈夫气概的合法的要求平等的热情,激励人们追求权力和荣誉。这种热情会把卑微者提升到伟大人物的行列;但是,在人类的心灵中也有一种对平等的卑劣憎恶,它驱使弱者将强者降低到与他们相同的水平,使人们宁可要奴隶制下的平等,也不要自由下的不平等。”
最近几十年中,美国民主党成了加强政府权力的首要工具,而在杰斐逊和许多他的同时代人的眼中,政府权力是对民主的最大威胁。这是字义变化的惊人证据。民主党是以促进“平等”的名义增加政府的权力的,而这种“平等”的概念,同杰斐逊认为与自由等同和托克维尔认为与民主等同的平等的概念,几乎截然相反。
当然,开国元勋的实践并不总是符合他们所宣扬的理论。最明显的言行不一,表现在奴 隶制问题上。托马斯·杰斐逊直到他死的那一天,即1826年7月4日,还拥有奴隶。他生前一再表示对奴隶制痛心疾首,他在笔记和通信中,都提过消灭奴隶制的计划,但他从未公开提出任何这种计划,也没有在竞选中反对过奴隶制。
然而,如果不废除奴隶制,他苦心建立的国家就将公然违背他所起草的《独立宣言》。因而毫不奇怪,在共和国最初的几十年中,关于奴隶制的论战越来越凶。这场论战的结果是一场内战。正如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讲演中所说,内战考验了“一个在自由中诞生的、以人生而平等为宗旨的……国家,能否长期坚持下去。”
这个国家坚持下来了。然而,是以无数生命、财产的损失和社会动乱为代价坚持下来的。
机会均等
内战一旦废除了奴隶制,人身平等——在耶和华和法律面前平等——接近于实现后,知识界讨论的重点和政府与私人政策的重点,就转到另一个概念,即机会均等上来了。
实实在在的机会均等——即所谓“同等”——是不可能的。一个孩子天生就是瞎子,而另一个则视力完好;一个孩子的父母从小就对他的幸福特别关心,提供良好的文化学习和智力发展的条件,而另一个孩子的父母则生活放荡,对孩子放任不管;一个孩子出生在美国,而另一个出生在印度、中国或苏联。显然,他们并不是生下来就享有同等的机会。而且,也无法使他们的机会同等。
同人身平等一样,机会平等也不能完全按字面来理解。它的真正含义的最好的表达也许是法国大革命时的一句话:前程为人才开放。任何专制障碍都无法阻止人们达到与其才能相称的、而且其品质引导他们去谋求的地位。出身、民族、肤色、信仰、性别或任何其他无关的特性都不决定对一个人开放的机会,只有他的才能决定他所得到的机会。
按照这种解释,机会均等只不过是更具体地说明人身平等和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含义。与人身平等一样,机会均等之有意义和重要,正是因为人们的出生和文化素质是不同的,因此,他们都希望并能够从事不同的事业。
同人身平等一样,机会均等与自由并不抵触。相反它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有些人仅仅因为某个种族出身、肤色或信仰而受到阻挠,得不到他们在生活中与他们相称的特定地位的话,这就是对他们的“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干涉。这就否定机会均等,也就是为一些人的利益牺牲另一些人的自由。
象每一种理想一样,机会均等很难完全得到实现。毫无疑问,对这一原则的最严重的背离是在黑人问题上,特别是在南方,但在北方也不例外。然而,在为黑人和其他集团取得机会均等方面,也有巨大的进步。“大熔炉”的概念正是反映了机会均等的目标。另外,大、中、小学“免费”教育的扩大,也反映了这一目标,尽管这种扩大,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并不纯粹是好事。
内战后,在公众普遍接受的价值等级中,机会均等居于优先地位,这特别表现在经济政策上。当时流行的字眼是自由企业、竞争和自由放任主义。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做任何生意,从事任何职业,购买任何财产,只需得到交易对手的同意。干得成功,他就有发迹的机会。但如果失败,就要自食其果。那时没有任何专制障碍。成败的关键是个人的才能,而不是出身、信仰或民族。
一个必然的结果是:被许多自认为是学者名流的人斥之为庸俗唯物主义的东西获得了发展。庸俗唯物主义强调金元万能,以财富为成功的标志。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这种强调反映了人们不愿意接受传统的看重出身和门第的封建贵族社会的标准。着重点明显地换成个人的才能,而财富的积累则是衡量才能的最方便的尺度。
另一个必然的结果自然是人的能力获得了巨大解放,它使美国成为生产率日益提高、越来越生气勃勃的社会。在这里,社会的流动成为日常的现实。还有一个可能令人吃惊的必然结果,就是慈善事业蓬勃兴起。这同财富的迅速增长是分不开的。在当时占优势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下,特别是由于对机会均等的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采取了以下特有的形式:如非营利的医院、私人资助的院校以及旨在帮助穷人的各种慈善机关。
【按:北宋中期及晚明时期的中国也是如此。】
当然,在经济领域同在其他领域一样,现实同理想并非总是一致的。当时政府的作用被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对企业没有设置严重障碍。到十九世纪末,政府采取积极措施,特别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来消灭竞争中的私人障碍。但是,一些不受法律约束的传统,继续妨碍着人们进入某些行业或从事某些职业的自由,而且毫无疑问,社会传统使那些出生在“正统”家庭、生来就有“正统”肤色,而且信奉“正统”宗教的人享有特别有利的条件。然而,各种不那么有特权的人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迅速提高表明,这类障碍决不是不可逾越的。
就政府的措施而言,对自由市场的主要背离在对外贸易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把为保护本国工业而征收关税看作是美国方式的一部分。关税保护同彻底的机会均等(见第二章)是不一致的,而且与自由移民也是不一致的。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除东方人外,世界各地的人均可自由移居美国。然而,人们可以为这种背离寻找国防需要方面的理由,也可以提出另一个性质很不相同的理由,即平等只限于国内。这后一种理由是不合逻辑的,但今天却被大多数鼓吹另一种平等的人所采用。
结果均等
那另一种平等即结果均等,是在本世纪深入人心的。它首先影响了英国政府的政策,继而影响到欧洲大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它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某些知识分子中,结果均等成了宗教信条:大家应当同时停止竞赛。正象《艾丽丝漫游记》中的渡渡所说:“人人获胜,都该得奖。”
这一概念同另外两种概念一样,“均等”也不能按字面解释为“等同”。其实,谁也不主张不问年龄、性别或身体素质,人人都分得同样份额的食品或衣服等等。虽然所要达到的目标相当“公平”,但“公平”却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一个确确实实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给以精确定义的概念。“对所有人公平分配”是取代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新口号。
结果均等的概念与前两个概念有着天壤之别。促进人身平等或机会均等的政府措施增大自由;致力于“对所有人公平分配”的政府措施减少自由。如果人民的所得依“公平”来定,又由谁来决定什么是“公平的”呢?就象大家同声问渡渡的:“可是谁来发奖呢?“”公平”一旦离开比较的对象,就不成为客观决定的概念了。“公平”如同“需要”一样,全在怎么看。如果所有人都要“公平份额”的话,那就必须由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来决定什么样的分配是公平的,而且他们必须能够把他们的决定强加给别人,从财产多于“公平”份额的人那里拿走一部分,给予财产少于“公平”份额的人。那些作决定并强加于人的人与听从他们决定的人能是平等的吗?我们不就进了乔治·奥韦尔的《动物饲养场》了吗?在那里,“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另外,如果人们的所得是靠“公平”而不靠他们所生产的东西来决定,“奖品”又从哪里来呢?还能有什么刺激人们去工作和生产呢?怎样决定谁来当医生,谁当律师,谁捡垃圾,谁扫街呢?由什么来保证人们接受分配给他们的任务,并按他们的能力来完成呢?显然,只有靠强力或强力威胁。
这里的关键不光是实践会同理想分离。同另外两种有关平等的概念一样,它们当然是要分离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公平分配”或其前身“按需分配”的理想与人身自由的理想之间有着根本的冲突。在人们试图使结果均等成为社会组织的最高原则的所有尝试中,都存在着这种冲突。其无法避免的最终结果是恐怖国家的出现:苏联、中国以及新近的柬埔寨可以说是清楚而令人信服的例证。而且,即便采取恐怖手段,也不曾使结果均等。在上述的每个国家中,无论拿什么标准来衡量,都存在着广泛的不平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仅在权力上,而且在物质生活上都不平等。
西方国家在促进结果均等的名义下采取的远不那么极端的措施,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只是程度稍轻罢了。它们也限制个人的自由,但它们同样没有达到其目标。这说明要把“公平份额”按普遍能接受的方式规定下来,或使社会成员对所受到的“公平”待遇感到满意,是不可能的。相反,越是试图扩大结果均等,越会激起人们的不满情绪。
推动结果均等的道德热情,大部分来自一种普遍的信念,即认为一些孩子仅仅因碰巧父母有钱就比其他孩子优越是不公平的。这当然是不公平的。然而,不公平可采取多种形式。它可以采取财产继承形式,如继承债券、股票、房产和工厂,也可采取天资继承的形式,如继承音乐才能、体力、数学天才等。财产继承比天资继承更容易遭到干涉。但从伦理的角度来看,这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呢?然而,许多人对财产继承感到愤恨,而对天资继承却不在乎。
现在,让我们从做父母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想使你的孩子一生中有较高的收入,那你可以采取各种方法做到这一点。你可以花钱让他(她)受教育,使他(她)有条件从事高收入的工作;或者,你可以为他开个店,使他能得到高于受雇人员的收入;你还可以给他留下一笔财产,让他靠财产收入过富裕日子。从伦理上看,这三种运用财产的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呢?再说,如果国家在课税后给你剩下任何钱的活,难道国家只允许你拿它过放荡的生活,而不准你把钱留给你的孩子吗?
这里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是微妙而复杂的,不能用“对所有人公平分配”那种简单化的公式来解决。因为,假如我们当真那么做的话,我们就得给予音乐才能差的青年最大量的音乐训练,以弥补他们天分之不足;而对那些音乐天分高的青年,却要剥夺他们受到良好音乐训练的机会;在个人天资继承的其他方面,也是一样。这样做对于天资差的青年可能是“公平”的,但对于天资好的青年,这是否“公平”呢?更不必说那些不得不为支付训练天资差的青年而工作的人,或者那些本可以从培养有才华者得到好处却因此得不到的人们了。
生活就是不公平的。相信政府可以纠正自然产生的东西是诱人的。但是,认识到我们正是从我们所哀叹的不公平中得到了多少好处,也同样是重要的。
马琳·迪特里希天生一对诱人而美丽的大腿,穆罕默德·阿里天生就有使他成为拳王的本事,这没有什么公平可言。但就另一方面讲,千百万喜欢看马琳·迪特里希的大腿或阿里的拳赛的人,却从自然界不公平地产生了迪特里希和阿里这件事中得到了好处。如果世界上的人都是一个样,这个世界还成什么世界呢?
穆罕默德·阿里一晚上能挣数百万美元,这肯定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为了追求某些抽象的平等理想,不允许阿里一个晚上的拳击(或每天为这场拳击进行的准备)的所得,比一个最底层的人在码头上干一天粗活挣得多的话,这对于那些喜欢看他比赛的人来说,岂不是更不公平吗?就算能够这样做,但其结果将是剥夺人们欣赏阿里拳技的机会。如果把给阿里的报酬限于码头工人一样的水平,我们很怀疑阿里还会忍受赛前的艰苦训练,并投身他经历过的那种搏斗。
公平这一复杂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可以通过赌牌这类碰机会的玩意儿来说明。晚上纸牌开局的时候,各个赌家的筹码的数量是相等的。但玩了一段时间后,数量就会不相等了。当晚收局时,某些人成了大赢家,另一些人成了大输家。按照平等的理想,是不是赢家得把赢的钱还给输家呢,如果真是这样,游戏就会变得毫无趣味,连输家也会觉得没意思。他们也许会玩上一两次,但如果他们知道,不论输赢,收局时还会同开局时一样的话,他们还会再玩吗?
这一例子同现实世界的关系,可能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大得多。每天,我们各自都要做出一些决定,碰碰机会。有时是大的机会,如决定从事什么职业,与谁结婚,买房子还是作一笔大的投资。更经常的是一些小的机会,如决定去看什么电影,在不在交通拥挤的情况下横穿马路,买这种保险还是那种保险。每次的问题在于由谁来决定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这个问题又取决于谁承担这些决定的后果。如果是我们承担后果的话,我们就可以作决定。但如果是别人承担后果的话,那么,该由我们或者能够由我们来做决定吗?如果你用另外一个人的钱,替他打牌的话,他会允许你自由作出决定吗?他不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你作出决定的权力,而且定下一些规矩让你遵守吗?再举一个全然不同的例子:如果政府(即你的纳税伙伴们)负责补偿洪水给你的房屋造成的损失,那还能够由你自由决定把房子再建到洪水淹了的平原上吗?政府对个人决定的干涉随着“对所有人公平分配”的运动的开展而不断增加,这并非是偶然的。
人民自己作出抉择并承担这些决定的大部分后果,这是贯穿着我国大部分历史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在过去二百年间刺激了福特家族、爱迪生家族、伊斯特曼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彭尼家族去改造我们的社会。正是这种制度刺激了另一些人,使他们乐意担风险、掏钱来资助这些野心勃勃的发明家们和产业大亨们从事冒险事业。当然,一路上有许多失败者,失败者也许比成功者要多。他们的名字被人遗忘了。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是甘愿冒风险的。他们知道自己是在碰机会。而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整个社会由于他们愿意碰这个机会而得到了好处。
这个制度所生产的财富主要来自发展新的产品或服务,来自生产这些产品或服务的新方法,也来自广泛分配这些产品或服务的新方法。由此给整个社会增加的财富和给人民群众增加的福利,要比这些创业者积累的财富多许多倍。亨利·福特发了大财,而国家得到了一种廉价而可靠的运输工具和成批生产的技术。另外,个人财富最后大部分还是用在社会福利上。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只是无数私人慈善活动中最为著名的。这些私人慈善事业是一个符合“机会均等”和“自由”的制度运行的突出结果。这里的“机会均等”和“自由”,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意义上的均等和自由。
我们只需要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海伦·霍罗威兹在一本论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1907年芝加哥文化慈善事业”的书中写道:
“在上世纪初和本世纪末,芝加哥是个被各种相互对立的力量推动的城市:它一方面是一个经营工业社会生产的基本商品的商业中心;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文化事业蒸蒸日上的地方。正如一位评论家说的,这个城市是‘一个猪肉和柏拉图的奇怪的混合体。’
“芝加哥文化运动的主要表现,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建立起了该城的一些伟大的文化机构,如艺术研究所、纽伯里图书馆、芝加哥交响乐团、芝加哥大学、费尔德博物馆、克里勒图书馆。……
“这些机构是该城市的新气象。无论最初建立时的动机是什么,它们大部分是由一伙工商业者所组织、维持和控制的。……尽管是由私人支持和管理,这些机构却都是为整个城市设计的。它们的托管人转向文化慈善事业,主要不是为满足个人对艺术或学术的向往,而是为了达到社会的目的。这些工商业者受到他们无法驾驭的社会势力的困扰,满怀文化的理想主义情绪,把博物馆、图书馆、交响乐团和大学看作是净化城市和发动城市(文艺复兴)的手段。”
慈善事业绝不仅仅限于文化机构。正如霍罗威兹在另一处写道的,这是“一种在许多不同方面爆发的活动”。芝加哥并不是孤立的例子。用霍罗威兹的话来说,“芝加哥似乎是美国的缩影”。正是在这一时期,在简·亚当斯的倡导下,芝加哥建立了赫尔贫民习艺所。赫尔贫民习艺所是在全国建立的许多贫民习艺所中的头一个。这些贫民习艺所是用来在穷人中传播文化和教育,并帮助他们解决日常问题的。另外,在这期间还建立了许多医院、孤儿院和其他慈善机构。
在自由市场制度与追求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目标之间,或在自由市场制度与对不那么幸运者的同情之间没有相抵触的地方,不管这种同情采取十九世纪私人慈善活动的形式还是采取二十世纪越来越多的通过政府来援助的形式——只要它们都反映一种帮助他人的愿望。由政府援助穷人的两种形式表面看上去相似,其实有天渊之别:第一种形式是,我们90%的人都赞同自己纳税来帮助处于底层的10%的人。第二种形式是,80%的人投票赞成让处于最上层的10%的人纳税来帮助处于最底层的10%的人。这就是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关于由B和C来决定D应为A做些什么的著名事例。第一种形式可能是明智的,也可能是不明智的;可能是帮助不幸者的有效率的方法,也可能是缺乏效率的方法。但是,它与机会均等和自由的信仰是一致的。第二种形式追求结果均等,与自由是完全对立的。
哪些人赞成结果均等?
支持结果均等这个目标的人寥寥无几,尽管在知识分子中,它简直成了宗教信条,在政治家的演说和各项法律的序言中被大肆宣扬。政府、最狂热信奉平等的知识分子们以及一般大众的所作所为,都使这种关于结果均等的谈论变成空话。
【按:文化马克思主义是马教版本的“新教”或“逊尼派”。】
拿政府来说,一个明显的事例是对彩票和赌博的政策。人们普遍而且正确地认为,纽约州特别是纽约市,是平等情绪的堡垒。然而,纽约州政府就经营彩票,并为赛马中的赌博提供方便。为引诱市民购买彩票和在赛马中打赌,它大作广告,以便为政府捞得巨额利润。同时,它尽力压制“数字彩票”赌博,因为“数字彩票”赌博比政府彩票更有赢头(特别是考虑到赢家容易逃税)。英国即使不是平等思想的发源地,也是平等思想的堡垒,但它却允许开设私人赌场,允许在赛马和其他体育项目中进行赌博。赌博确实成了一种全国性的娱乐活动和政府收入的一大来源。
拿知识分子来说,最清楚的证明是他们未能把他们那么多人宣扬的事付诸实践。可以由他们自己亲自试一试怎样实行结果均等。首先得确定所谓均等指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在美国国内实行,还是在整整一批选定的国家内实行,还是在整个世界实行?以哪种收入作标准?个人的?家庭的?一年的?十年的?还是一生的?是单指货币形式的收入呢?还是也包括下面这样一些非货币的项目,如自有自住的房屋、自种自食的粮食、家庭成员尤其是家庭主妇的非花钱雇用的服务?身体和智力的优劣又怎么算?
无论你如何断定这些问题,只要你是平等主义者,就可以估计出什么样的货币收入符合你的平等概念。如果你的实际收入高于这个标准,你可以留下标准内的部分,把多余的部分分给收入低于这一标准的人。如果你的标准要包括全世界,象大多数平等主义言论所主张的那样,那么,每人的年平均收入将低于二百美元(以1979年美元价值计算),这个数量将是符合大多数平等主义言论所讲的平等概念的。这大约是全世界平均每人的收入。
欧文·克里斯托尔的所谓“新阶级”:即政府官僚、由政府基金资助进行研究或由政府资助的“智囊团”雇用的学者、许多所谓“总体利益”或“公共政策”集团的成员、记者和从事新闻事业的其他人员,都是平等学说最热烈的鼓吹者。然而,他们使我们想起了关于公馆会教士们的一个古老的(如果是不公正的话)谚语:“他们到新世界来行好,结果自己过得挺好。”新阶级的成员总的来说属于社会上挣钱最多的人,而且,对于其中许多人来说,宣扬平等,设法通过并实施这方面的法律,已证明是得到这种高收入的有效手段。我们大家都容易把自己的福利等同于社会福利。
当然,平等主义者可能会提出抗议,说他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如果别人都被迫那样做的话,他将乐意拿出他认为超过平等水平的那部分收入来重新分配。一方面,认为强制手段将改变事态的看法是错误的——即使其他人都这样做,他对别人收入的贡献也仍将只是沧海一粟。不论他是唯一的捐献者还是许多捐献者中的一个,他个人的贡献总是那么大。的确,他可以把他捐的钱直接给予那些他认为是合适的接受者中最贫穷的人,从而使他的捐献成为更有价值的事。另一方面,强制手段将使事态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这类再分配行动是自愿的话。将要出现的社会将同强迫人们进行再分配而出现的那种社会截然不同。按照我们的标准,前一种社会比后一种社会好千百倍。
如果有人认为实行强制性平等的社会更可取,那他们可以亲身实践一下。他们可以加入我国或其它国家的许多现有的公社,也可以建立新的公社。而且,任何一批希望这样生活的人能够自由地这样做,当然是完全符合人身平等、机会均等和自由等信念的。我们的论点,即对结果均等的支持不过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从希望参加那种公社的人数之少,和那些已经建立的公社之脆弱,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美国的平等主义者可能会反驳说,公社的数量少和脆弱是一个“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对它们进行污蔑和因此而使它们受到歧视的结果。这在美国可能是真的,但是,正如罗伯特·诺吉克所指出的,在有一个国家这不是真的,那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在那里,恰恰相反,平等主义公社受到高度重视和赞赏。在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定居的早期,集体农庄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继续在以色列国中发挥重要作用。以色列国领导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成员非但不会受到非议,反而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人们的欢迎。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加入或离开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是有活力的社会组织。然而,不论在任何时候,肯定也包括今天,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人从未超过以色列犹太人口的5%。我们可以把5%这一比例看作是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最多人数,这部分人自愿选择一种强制实行结果均等的制度,而不愿要不平等的、多样性的和有机会的制度。
公众对于累进所得税的态度各不相同。最近,在一些还没采用累进所得税的州曾就征收这种税进行了公民投票,在另外一些州则就提高累进率进行了公民投票,结果一般都被否决了。另一方面,联邦所得税的累进率则很大,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尽管它也包含许多实际上可以大大降低累进率的条款(即“漏洞”)。这表明,公众对于重新分配适当数量的税收还是能够容忍的。
但是,我们要冒昧地说一句,人们对雷诺、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的喜爱,也同样真实地反映了公众的偏好,其真实程度丝毫不亚于联邦所得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社论以及《纽约书评》所反映的情况。
平等政策的后果
我们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我们与它们具有共同的知识和文 化背景,我们的许多价值概念都来源于它们。英国可能是最有启发性的例子。它在十九世纪实行机会均等方面以及在二十世纪实行结果均等方面,都起了表率作用。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的国内政策,一直为寻求更广泛的结果均等所左右。政府采取了一项又一项措施,旨在从富人手里拿走一些财富,分配给究人。所得税率不断提高,最后提高到占不动产收入的98%和“所挣”收入的83%,而且遗产税也越来越重。在向失业者和老年人提供救济的同时,国家还大规模地增加了医疗、住房和其他福利事业。不幸的是,其结果与那些对几世纪来一直占优势的阶级结构十分恼火的人所希望的大不相同。虽然财富被广泛地重新分配,但到头来分配还是不公平。
实际上只是产生了新的特权阶级来代替或补充原有的特权阶级。新的特权阶级包括:握有铁饭碗的官僚们,不论在职期间还是退休之后,他们都受到保护,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工会头头们,即劳工运动的贵族,他们自称为最受压迫的工人讲话,但实际上他们却是这块土地上收入最高的工人;还有新的百万富翁们,他们善于规避从国会和官僚机构中倾泻出来的法律和规章,他们想方设法地逃税漏税;并把财产转移到收税官力所不及的海外去。如果说这是收入和财富的巨大改组,那倒是真的;但如果说这是更大的平等,却不大象。
平等运动在英国失败,并不是由于采取了错误的方法,尽管某些方法的确是错误的;不是由于管理不善,尽管某些方面的管理的确很糟;也不是由于管理人员无能,尽管某些管理人员的能力的确很差。平等运动的失败有其更为根本的原因。它违背了人类的一个最基本的天性,即亚当·斯密所说的,“每个人都为改善自身的境况而作一贯的、经常的和不间断的努力。”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人们也为改善其子孙后代的境况而努力。当然,斯密所说的“境况”不单指物质福利,尽管物质福利肯定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所想的是更为广阔的概念,这一概念包括了所有人用来判断自己成就的价值标准,特别是那种在十九世纪曾促使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社会价值标准。
当法律妨碍人民去追求自己的价值时,他们就会想办法绕道走。他们将规避法律,违反法律,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道德规范,认为强迫人们为他们不赞成的目的交出自己创造的许多东西去帮助不认识的人是合理的。当法律同大多数人认为是合乎道德的而且正当的准则发生矛盾时,他们就会违反法律,不论这种法律是在促进平等这样高尚的理想的名义下通过的,还是赤裸裸地为一个集团的利益而牺牲其他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守法,只是出于害怕受到惩罚,而不是出于正义感和道德观念。
当人们开始违反某一类法律时,不守法的情况就会不可避免地波及所有的法律,甚至影响到那些公认为是合乎道德的和正当的法律,如反对暴力、盗窃和破坏行为的法律。说来也许难以置信,近几十年中,英国有增无减的犯罪活动,很可能正是平等运动的后果。
另外,平等运动把一些最有才能的、最训练有素的、最生气勃勃的公民赶出了英国,而使美国和别的国家大受其益,它们使这些人有更好的机会为自己的利益发挥才能。最后,谁能怀疑平等运动对工作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就是英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经济增长方面大大地落后于它的欧洲邻国、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美国在促进结果均等方面没有英国走得那么远。然而,许多同样的后果已经显露出来了:例如,促进平等的措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财富以决非平等的方式进行再分配,犯罪率上升,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下降。
资本主义和平等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存在着收入和财富的严重的不平等。这使我们大多数人感到愤慨。看到一些人在奢侈挥霍,另一些人则饱尝贫困的煎熬,谁都会感慨万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流传着一种神话,说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即我们所说的机会均等,加深了这种不平等,在这种制度下是富人剥削穷人。
没有比这更荒谬的说法了。凡是容许自由市场起作用的地方,凡是存在着机会均等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都能达到过去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水平。相反,正是在那些不允许自由市场发挥作用的社会里,贫与富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宽,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种情况发生在社会地位可以世袭的封建社会,如中世纪的欧洲、独立前的印度以及现代南美洲的许多国家。也发生在社会地位取决于能否进入政府部门的实行中央计划的社会,如俄国、中国和独立后的印度。甚至发生在象这三个国家那样以促进平等的名义引入中央计划的社会。
俄国是一个由两部分人组成的国家:一边是官僚、共产党官员、技术人员组成的一小撮上层特权阶级,另一边是今天的生活比他们的祖先好不到哪儿去的广大群众。上层阶级可以进入特殊商店和学校,可以得到各式各样的奢侈品;而广大群众却注定只能享受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我记得有一次在莫斯科看到一辆大型轿车,就向向导打听它的价钱,向导说:“噢,那不出售,是专供政治局委员用的。”最近由美国记者写的几本书,极为详细地记录了俄国上层阶级的特权生活同广大群众贫困生活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下层,俄国工厂里的一个工头与一个普通工人在平均收入上的差距,也比在美国工厂大。无疑,苏联工头的收入应该更高些,因为美国工头担心的毕竟只是被解雇,而苏联工头还要担心被枪毙。
另外,中国也是一个在有政治权势的人与其他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里一些工人与其他工人之间收入悬殊的国家。一位敏锐的中国问题学者曾经写道:“ 1957 年在中国的富庶地区与贫穷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可能比世界上除巴西外的任何较大国家都大。”他援引另一位学者的话说:“这些例子说明,中国工业部门的工资结构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工资结构平等多少。”他在总结他对中国的平等的考察时说:“中国今天的收入是怎样平均分配的呢?肯定不如台湾或南朝鲜来得平均。……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收入分配又显然要比巴西和南美洲平均……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远非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事实上,中国在收入上的差别可能要比一些公认为是‘法西斯’分子当权而广大群众遭受剥削的国家大得多。”
【按: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于西元 1956 年。】
工业的进步、机器的改进、所有新时代的伟大奇迹,对于有钱人来说,关系较少。古代希腊的富翁,从现代的供水管道得不到什么好处:有跑步的仆人提水代替自来水。电视机和收音机也不足道,罗马的贵族们能够在家里享受到最好的乐师和演员的表演,能够把最出色的艺术家留在家里。现成的服装、超级市场和其他许多现代文明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不了什么色彩。他们也许欢迎运输和医疗上的改进,而其他一切西方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主要是增长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这些成就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方便和乐趣,而在过去,这些只是富人和权势者专有的特权。
1848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道:“迄今为止,所有机器发明是否减轻了人们日常的艰苦劳动,是很值得怀疑的。机器发明使更多的人过单调乏味的生活,也使更多的制造商发财致富,同时增加了中产阶级的舒适。按其性质来说,机器发明必将使人类命运发生重大变化,但目前还没有带来重大变化。”
【按:穆勒这厮思想确实很成问题。詹姆斯·斯蒂芬批评得很恰当!】
今天谁也不能再说这种话了。只要从工业世界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就会发现,目前仍然从事极艰苦劳动的,几乎只有那些开展体育活动的人。要找到日常的艰苦劳动没有被机器发明所减轻的人,那你只有到非资本主义世界去找:俄国、中国、印度、孟加拉国以及南斯拉夫的一些地区;或者到较为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去找:非洲、中东、南美洲,以及前不久的西班牙或意大利。
结论
一个社会把平等——即所谓结果均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使用强力来达到平等将毁掉自由,而这种本来用于良好目的的强力,最终将落到那些用它来增进自身利益的人们的手中。
另一方面,一个把自由放在首位的国家,最终作为可喜的副产品,将得到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尽管更大的平等是副产品,但它并不是偶然得到的。一个自由的社会将促使人们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精力和才能,以追求自己的目标。它阻止某些人专横地压制他人。它不阻止某些人取得特权地位,但只要有自由,就能阻止特权地位制度化,使之处于其他有才能、有野心的人的不断攻击之下。自由意味着多样化,也意味着流动性。它为今日的落伍者保留明日变成特权者的机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使从上到下的几乎每个人都享有更为圆满和富裕的生活。
本节内容概述
结果均等:每个人应享有同等水平的生活或收入,而且应该结束竞争。结果均等显然是与自由相抵触的。努力推进这种均等,是造成政府越来越大并使我们的自由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
同人身平等一样,机会平等也不能完全按字面来理解。它的真正含义的最好的表达也许是法国大革命时的一句话:前程为人才开放。任何专制障碍都无法阻止人们达到与其才能相称的、而且其品质引导他们去谋求的地位。出身、民族、肤色、信仰、性别或任何其他无关的特性都不决定对一个人开放的机会,只有他的才能决定他所得到的机会。
成败的关键是个人的才能,而不是出身、信仰或民族。
生活就是不公平的。相信政府可以纠正自然产生的东西是诱人的。但是,认识到我们正是从我们所哀叹的不公平中得到了多少好处,也同样是重要的。
一个社会把平等——即所谓结果均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使用强力来达到平等将毁掉自由,而这种本来用于良好目的的强力,最终将落到那些用它来增进自身利益的人们的手中。
另一方面,一个把自由放在首位的国家,最终作为可喜的副产品,将得到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尽管更大的平等是副产品,但它并不是偶然得到的。一个自由的社会将促使人们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精力和才能,以追求自己的目标。它阻止某些人专横地压制他人。它不阻止某些人取得特权地位,但只要有自由,就能阻止特权地位制度化,使之处于其他有才能、有野心的人的不断攻击之下。自由意味着多样化,也意味着流动性。它为今日的落伍者保留明日变成特权者的机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使从上到下的几乎每个人都享有更为圆满和富裕的生活。
第6章 我们的学校出了什么问题?
教育一直是美国梦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教徒的新英格兰,学校很快建立了起来。起初作为教会的附庸,而后为世俗的官方所接管。伊利运河通航之后,农民们离开了新英格兰的山区,来到富饶的中西部平原。他们在所到之处,建立起一所所学校。不仅建立了中、小学,还建立了大学和神学院。许多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从大西洋彼岸来的移民,都渴望接受教育。大多数人在他们定居的主要都市和大城市内,都不轻易放过任何受教育的机会。
最初的学校是私立的,上学全凭自愿。渐渐地,政府开始发挥较大的作用。先是在财政上给予资助,继而是建立和管理官办学校。1852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第一个强迫入学的法令,而所有的州都实行强迫入学制则是在1918年。一直到二十世纪,政府对教育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地方当局来实施的,盛行的是地区学校,由当地的学校管理委员会控制。接着,开始了所谓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主要是由于大城市内不同教学区之间的种族成分和社会成分差异太大而引起的。另外,这场运动也受到职业教育家希望发挥更大作用的影响。随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政府的扩大和权力的集中,这场运动也不断发展。
为所有人提供的、广泛的普及教育,以及为同化我们社会的新成员的公立教育,在防止分裂活动和使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能够和睦相处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对此,我们一直,而且确有理由引为自豪。
遗憾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的教育越来越走下坡路。家长们抱怨子女们所受教育的质量下降了。很多人对孩子们的身体健康越发感到担忧。老师们抱怨说,他们所处的教学环境,往往不利于孩子们学习。越来越多的老师在教课时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纳税人抱怨费用上涨。几乎没有人认为我们的学校是在向孩子们传授他们所需要的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与促进同化及创造和睦气氛的愿望相反,学校越来越成为我们从前极力避免的分裂的源泉。
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在靠近主要城市的一些富人居住的郊区,学校办得很好,许多小城镇和乡村办的学校也很出色或令人比较满意,但一些大城市内的学校则糟得令人难以置信。
“在公立教育事业中,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黑人儿童的教育,无疑是成绩最糟糕、失败最惨重的领域。与其说是使黑人儿童受教育,还不如说是使他们失掉受教育的机会。但按照政府的一贯说法,公立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却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由此看来,公立教育的确是一个双重悲剧。”
据我们看,公立教育所患的病与我们在前面和后面章节中所谈到的许多福利计划患的病是相同的。四十多年前,沃尔特·李普曼把它确诊为“社会集权过度症”,其病因在于“信念的改变,以前人们认为,由那些思想狭隘的和自以为是的人自由行使权力会很快带来专制、反动和腐朽”,……要取得进步就必须限制统治者的作用和权力,而现在人们则认为,“统治者的能力是无限的,因此,不应对政府的权力施加任何限制。”
在培养孩子方面,这种病症的表现是:作父母的无法干预孩子受什么样的教育,他们既不能直接出学费为孩子挑选学校,也不能间接地通过开展地方政治活动来改变教育制度。学校的控制权已经落到了职业教育家手中。尤其在大城市里,学校权力的日益集中和官僚主义的增加,更加重了这种病症。
在高等教育方面,私人市场的作用要比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大一些。但在那里也摆脱不了过分集权的社会的弊病的影响。1928年,在高等教育中,上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比上私立学校的学生少。1978年,上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了三倍。由于学生自己交付学费,政府在直接筹资方面的作用落后于政府在管理方面的作用。然而,尽管如此,1978年政府的直接拨款已经超过了由公立和私立学校组成的高等教育的总经费的一半。
同对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影响一样,政府作用的增加对高等教育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它所创造的环境使尽职的老师和用功的学生都难以安心学习。
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问题所在
甚至在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年代里,就已经不仅是城市有学校,而且几乎每一个小镇、村庄和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有学校。在许多州或地方都有法律明文规定要建立一所“公立免费学校”。但是,大多数学校是靠学费和私人资助来办的。市、县或州政府一般只提供一些补充资金,补足那些父母无力交纳学费或所交学费不足的孩子们的上学费用。尽管当时受教育既不是强迫性的也不是自由的,但实际上是普及的(当然,奴隶们除外)。纽约州公立学校的校长在1836年的一份报告中说:“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有理由认为,在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和专科学校受教育的孩子的人数,与五岁至十六岁孩子的总人数相等。”当然,州与州之间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总的来讲,白人家庭的孩子,不论其家庭经济条件如何,都受到了教育。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人们发动了一场运动,要用所谓免费学校来代替形形色色的私立学校。也就是家长和其他人不直接交学费,而是用纳税的方式间接向学校交学费。E.G.韦斯特广泛研究过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作用的发展情况,他认为,这场运动并不是由对教育现状感到不满的家长们发起的,而“主要是由教员和政府雇员们”发起的。免费学校运动最著名的参加者是霍勒斯·曼,在《大英百科全书》中,他被称为“美国公共教育之父”。霍勒斯·曼曾任1837年设立的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的第一任秘书长。在这以后的十二年中,他领导了一场气势磅礴的运动,争取建立一种由政府出资、由职业教育家管理的中小学教育制度。他的主要论点是,教育非常重要,因此政府有责任向每个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学校应办成非宗教性质的,应接纳所有来自不同信仰、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种族的家庭的孩子。这种普及的免费教育可以使孩子们克服由于父母贫穷造成的不利条件。“在向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霍勒斯·曼反复强调……教育是一种最好的、一本万利的公共投资。”尽管这些论点都是在增进公众利益的名义下提出的,但教育和行政管理人员对公立学校运动的支持,大部分出于自私自利的狭隘动机。他们期望,由于是由政府而不是由学生的家长直接交学费,他们将得到更牢靠的职业、更有保障的薪金收入以及对教育更大的控制权。
“尽管困难巨大,障碍重重,……但霍勒斯·曼所提倡的这种教育制度的主要轮廓在十九世纪中叶却被勾画了出来。”
从那时起,大多数孩子都上了公立学校。只有少数学生继续在所谓私立学校念书,私立学校大都是由罗马公教会或其他教会开办的。
学校体制发生了变化:以前是私立学校占多数,现在是公立学校占多数,但这一变化并不仅仅发生在美国。正如一位权威人士所说,“人们逐渐接受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教育应当是国家的职责”。他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十九世纪意义最为重大的趋势。它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仍然影响到所有西方国家的教育事业。”十分有趣的是,这一趋势最初在1808年兴起于普鲁士,并几乎同时出现于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而英国是在美国之后才出现这一趋势的。“在自由放任主义的影响下,英国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允许国家干预教育事业。”最终建立起公立学校制是在1870年,一直到1880年才实行强迫性的初等教育,直到1891年才基本上废除学费。英国同美国一样,几乎在政府接管之前,教育就已经普及。韦斯特教授颇有根据地认为,在英国由政府接管教育正如在美国的情形一样,它并不是由于家长的压力所造成,而是由于教师、行政人员和好心的知识分子的压力所造成。他的结论是,政府的接管降低了教育质量,减少了教育的多样性。
教育同社会保险一样,也是证明极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有相似之处的一个例子。贵族专权的普鲁土和法兰西帝国都是国家管理教育的先驱。美国、英国和稍后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们,则是国家控制教育的主要支持者。
在美国,公立学校体制就如同被自由市场的汪洋大海包围的一个社会主义孤岛,它的建立只是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早期对自由市场和自愿交换的不信任。它最多不过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机会均等的理想的重视。霍勒斯·曼和他的助手们巧妙地利用这种强烈的情绪,在改革运动中获得了成功。
不用说,公立学校制度并不能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而只能看作是“美国式的”。决定该制度运行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非中央极权的政治结构:美国宪法严格地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使它无法发挥重大的作用。各州把控制学校的权力大部分都留给了地方团体、小市镇、小城市和大城市内的各个区。家长密切监视管理学校的政治机构,部分地代替了竞争,同时也确保了家长们的普遍要求得以实现。
在大萧条之前,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学校区得到巩固,教育区得到扩大,职业教育者的权力越来越大。大萧条过后,公众加入到知识分子的行列,开始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能力无限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单间教室的学校和地方学校委员会的衰败就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控制学校的权力,也就很快从较小的地方机构转给了较大的地方机构,如县、市、州一级的机构,最近则转给了联邦政府。
1920年,地方拨款占公立学校收入总额的83%,联邦拨款还不到1%。1940年,地方拨款下降到68%,而目前还不足一半。剩下的经费由州政府提供:1920年州政府拨款占公立学校收入总额的16%,1940年占30%,现在占40%以上。联邦政府拨款所占百分比虽然很小,然而增长迅速,目前已经从1940年的不到2%上升到8%左右。
由于职业教育者接管了教育的权力,家长的控制权被削弱了。另外,赋予学校的职责也改变了。人们仍然希望学校教会孩子们读、写、算,并向他们传授基本的价值概念。但是,现在学校还被认为是促进社会流动性、加强种族结合的手段,而且认为可以用它来达到其他一些与学校的基本任务关系甚少的目标。
在第四章,我们谈到过马克斯·甘蒙博士的“官僚替代论”,这是他考察完英国的全国卫生局后提出来的。用他的话来讲,在“官僚体制内……费用的增加将与生产的下降并驾齐驱。……这样的体制就象是经济宇宙中的‘黑洞’,它在吸收资源的同时,‘释放’的生产却在收缩。”
甘蒙的理论,完全适用于美国公立学校体制官僚主义的不断增长和权力的日益集中所产生的结果。自1971-1972学年至1976-1977学年的五年中,美国公立学校教职员工的总额增加了8%,以美元计算,每个学生的费用增加了 58%(扣除通货膨胀率后为 11%)。输入明显上升了。
学校学生人数下降 4%,同时,学校数目也减少了4%。我们相信,几乎没有读者会反对教育质量比数量下降得更厉害的说法。这是通过正式考试记录的成绩下降情况所说明的事实。输出明显下降了。
每单位输入量的输出减少,是不是由官僚主义的增长和权力的日益集中引起的呢?让我们来看下面的证据,学校区数目从1970-1971至1977-1978学年的七年中减少了17%,这可以说是权力日益集中的长期趋势的发展。至于官僚主义,我们来看稍早一些时候即1968-1969至1973-1974学年的情况,因为我们目前只能得到这段时期的资料。在这五年中,学生人数增加1%,专业人员总数增加15%,教师增加14%,而学监增加44%。
学校教育的问题并不仅仅同规模的大小有关,也就是说。学校区的扩大或每个学校学生人数的增加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因为事实证明,在工业中,规模庞大往往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改进质量。可以说,美国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大规模生产和经济学家的所谓“经济效果按规模递增”的原理。那么,为什么规模的大小对教育的影响不同呢?
其实并不是影响不同。问题并不出在教育同其他活动的区别,而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安排:是让消费者自由选择,还是让生产者说了算,而消费者没有发言权。如果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企业要想扩大,就得生产出消费者所喜爱的质高价廉的产品。企业单单靠规模庞大是不能把消费者不喜欢的产品推销出去的。通用汽车公司的庞大规模并不妨碍它继续发展。而格兰特公司的庞大规模也不能使它免于倒闭。在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只有当庞大规模产生效率时,它才能存在下去。
但一般来说,在各种政治安排中,规模的大小确实会影响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单个公民会感觉到,自己在较小的地区内比在较大的地区内对政治当局的所作所为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他可能不具有买东西时的那种选择自由,然而,他至少具有相当可观的机会去左右周围发生的事情。另外,假如有很多小地区的话,个人就可以选择在哪里生活。当然,这是牵涉到很多因素的复杂选择。尽管如此,它意味着地方政府必须向它的公民提供与他们所纳税款的价值相符的服务。否则,它就会被取代,或者失掉一些纳税人。
但是,当权力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时,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单个公民感到,自己对于高高在上的、缺乏人情味的政治当局没有,或很少有任何发言权。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的可能性虽然还存在,但已经是极为有限的了。
【按:这从侧面反映出要建设大同社会必须要重视地方自治。】
在学校教育中,家长和儿童是消费者,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是生产者。学校教育的集中化意味着教育单位的规模越来越大,消费者的选择能力越来越小,生产者的权力增加。教师、管理人员和联邦政府官员们同别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可能也是家长,衷心地希望有一个好的教育体制。然而,作为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联邦政府官员,他们的利益与他们作为家长的利益和他们所教的孩子的家长的利益是不同的。他们的利益是靠更大的集权化和官僚化来增进的。尽管这与家长的利益并不一致,然而,他们的利益确实是通过削弱家长的权力来增进的。
每当政府官僚们不顾牺牲消费者的选择来接管某件事时,就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情况在邮政方面、垃圾收集方面或其他章节所列举的许多例子中,比比皆是。
在学校教育中,我们中间那些高薪阶层的人们仍然享有选择自由。他们可以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他们实际上为孩子交两次学费。一次是为资助公立学校体制纳税,另一次是为自己孩子上学交学费。另外,他们也可以根据公立学校的质量,选择居住地点。好的公立学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比较富裕的郊区。在那里,家长对学校仍有控制权。
情况最糟的是大城市的城区,如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和波士顿等市的城区。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只有付出极大的努力,才交得起双重学费,因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只能让孩子上教会学校。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他们把家搬到有好学校的地方。他们的唯一办法是力图影响主管公立学校的政治当局。然而,这样做通常是徒劳的,或者是困难很大的,而且他们根本无力做这种事。市内居民在孩子的上学教育方面恐怕要比所有其他方面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唯一的例外也许是防止犯罪,这是政府提供的另一项“服务”。
具有讽刺意味而且十分悲惨的是,一个致力于使所有孩子掌握共同语言,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的制度,实际上却在加深社会的分化,而且造成了极不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市内每个学生的教育费往往与富裕郊区的一样高,但质量却差得很远。在郊区,几乎所有钱都用在教学上,而在市内的学校,经费大部分都花在维持纪律,防止破坏,或补偿破坏所造成的损失上。一些市内学校的环境象是监狱,而不是个学习的地方。就为使子女受教育而纳税而言,住在郊区的家长比住在市内的家长划得来。
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凭单计划
即便是在市内,学校并不一定非得是现在这种样子。过去,在家长有较大的控制权时,情况不是这样。今天,在那些家长仍能控制学校的地方,情况也不是这样。
美国人我行我素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提供了许多很好的例子,说明家长能有更多的选择时会出现什么情况。现举我们参观过的一个教会小学为例,该学校名叫圣约翰·克里索斯姆小学,位于纽约市布朗克斯区最贫穷的一个街道内。它的经费一部分来自一个叫做“纽约市奖学金基金会”的慈善机构,一部分来自罗马公教会,其余来自学生所交纳的学费。孩子们上这个学校,是家长的选择。这些孩子几乎都来自穷苦家庭。然而,他们的父母至少都要交纳一定数量的学费。这些孩子品行端正,求知欲强。教师专心任教。校园里非常宁静,没有噪杂的吵闹声。
甚至把那些身为修女的教师们所提供的无偿服务的费用计算在内,每个学生的花费也比公立学校的学生少得多。然而,这些孩子的平均分数却比公立学校的同年级学生高出两个等级。这是由于教师和家长可以自由选择如何教育孩子的方法。私人资金代替了税款,官僚手中的控制权被夺走,归还给了应该掌握控制权的人。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中等教育方面的例子。本世纪六十年代,哈莱姆区暴力活动猖撅。很多孩子离开了学校,一些为此而担忧的家长和教师决定设法改变这种情况。他们用私人资金买下了几家空店铺,办起了所谓沿街学校。其中最出色和最成功的一所,名叫哈莱姆预备学校,专门吸收不能用传统方法进行教育的年轻人。
哈莱姆预备学校缺乏足够的物质条件。很多教师不具有教公立学校所要求的文凭。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把事情办好。尽管许多学生过去功课很差,曾经中途退学,但是,在哈莱姆预备学校,他们找到了所期望的教育。
这所学校办得非常成功。许多学生考上了大学,而且有些考上了第一流大学。遗憾的是,它并没善始善终。在经历了最初阶段的经济危机的打击后,学校又面临着缺少现金的困难。教育委员会提出给予卡彭特(该校校长和创办人之一)一笔款子,条件是他今后按照该委员会的规章制度办事。在为保持独立性作了长期斗争后,卡彭特让步了。学校被官僚接管。“我觉得”,卡彭特先生评议道,“在教育委员会的僵化的官僚主义统治下,象哈莱姆预备学校这样的教育机构一定会夭折,不会发达兴旺的。……对于将要发生的一切,我们只能等着瞧。我不相信事情会有任何转机。我是正确的,自从我们隶属于教育委员会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不都好,也不都坏,但毕竟是弊多利少。”
这类私人冒险是有价值的。但它们最多只是触及了那些所要做的事情的皮毛而已。
一种能够取得较大进展的、把知识带回课堂的办法是,给予所有家长以较大的控制孩子教育的权力,就象我们中间那些高薪阶层的人们现在实际上具有的那样。这样做,对于那些目前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的父母,尤其重要。比起别人来,父母总是更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也更清楚自己子女的能力和需要。社会改革主义者,特别是教育改革主义者,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父母,特别是那些贫穷的、受过很少教育的父母,不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而且不具有为自己的子女选择教育的能力。这纯粹是无稽之谈。这样的父母确实很少有为子女选择的机会。但是,美国历史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一旦有机会的话,他们为了子女的幸福,总是愿意作出很大的牺牲,而且会作出很明智的选择。
无庸置疑,一些父母不太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缺乏明智地进行选择的能力和愿望。然而,他们是极少数。遗憾的是,我们的现行制度在帮助他们的子女方面所做的事,无论怎样说都是太少了。
一种既能保证父母享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又能保持现有的财政来源的简单、可行的方法是实行凭单计划。假设你的孩子正在上一所公立小学或中学。就全国范围来讲,1978年纳税人(你和我)平均要为每个入学儿童付大约两千美元。如果你让孩子从公立学校退学,转入私立学校,那你每年就为纳税人节省大约两千美元。但是,你得不到一点儿节省下来的钱,除非把这笔钱退给所有的纳税人,即使如此,你最多也只能少交几分钱税款。除去纳税外,你还得付私人学费,这就是促使你让孩子上公立学校的强大动力。
但是,假定政府对你说:“如果你不要我们为你的孩子出教育费,那你将会得到一张凭单,用这凭单你可以为孩子在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上学交纳一定金额的学费。”凭单上的金额可能是两千美元,或者,为了使你和其他纳税人都能分得节省下来的钱,也可能是一千五百或一千美元。但不论是二千美元还是少于这个数字,它至少可以解除一部分目前限制着家长选择自由的资金困难。
凭单计划所体现的原则正好同退伍军人领取教育津贴的原则一样。退伍军人可以得到一张只能用于教育的凭单。他可以拿这份钱随便挑选学校,只要这所学校符合政府所规定的某些标准。
家长也应被允许在任何一个愿意接受他的子女的学校使用凭单,不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也不论是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城市或州,还是在其他地区、城市或州。这样,不仅将给每位家长较多的选择机会,同时也迫使公立学校通过收学费而自筹资金(如果凭单金额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完全自筹资金;如果不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部分地自筹资金)。这样,不仅公立学校之间要展开竞争,而且还要同私立学校竞争。
这个计划并不减少任何人为教育纳税的负担。它只是在社会有责任向孩子们提供教育的前提下,给予家长较为广泛的选择余地,让他们自己决定孩子应受什么样的教育。这个计划也不会影响目前为私立学校规定的标准,这些标准是为实施强迫入学法而制定的。
我们认为,凭单计划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因为它既不影响教育经费,也不影响强迫入学法。我们主张走得更远一些。一般说来,社会越富裕,分配越平均,政府资助教育的理由就越少。无论如何,家长们担负了大部分教育费,而且毫无疑问,就获得相同的教育质量所花的费用来说,家长直接交学费要比通过纳税而间接承担教育费用来得便宜——除非教育活动同其他政府活动极不相同。然而,实际上,随着美国平均收入的提高和收入分配更加均等,政府资金在整个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重却越来越大。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是政府对学校的管理。父母的收入增加时,自然就想为孩子的教育多花些钱,但由于学校归政府管理,所以实现他们这种愿望的最简便方法就是增加公立学校的开支。凭单计划的一个优点在于它将鼓励更多的家长直接交纳学费。如果父母想在教育上多花些钱,那他们可以补足凭单金额,直接交纳学费。为救济困难学生的公共助学金仍会保留下来,但是,这同90%的孩子上学要靠政府的补助比较起来,情况是大为改观了,因为需要救济的困难学生只占5%或10%。
强迫入学法是政府掌握私立学校标准的根据。但我们弄不清,实行该法律本身有什么根据。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当我们最初泛泛谈到这个问题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实行这种法律,其理由是:“如果大多数公民不具备最低限度的文化和知识水平,一个稳定和民主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现在仍然相信这一理由。但是二十五年来关于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教育情况的研究报告表明,为获得最低程度的文化知识,大可不必采用强迫入学法。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类报告表明,在入学法实行之前,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几乎已经普及。在英国,实行强迫入学法和政府资助教育之前,中小学教育也已经几乎普及。强迫入学法同大多数法令一样,有利也有弊。我们不再相信利多于弊了。
我们意识到,这些关于政府资助教育和强迫入学法的观点对大部分读者来说也许是过于偏激了。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只是提出这种观点,而不要求读者给予全面支持的原因。我们主张实行凭单计划,这是摆脱目前做法的最稳妥的方法。
当前,唯一最有可能代替地方公立学校的是教会学校。因为只有教会能够大规模地资助学校教育,而只有得到资助的学校教育才能与“免费”学校教育相竞争。(试图出售别人丢掉的产品!)凭单计划将提供各种各样的替代物,如果它们不被政府“批准”所要求的极其死板僵硬的标准扼杀掉的话。人们在公立学校之间的选择机会将会大大增加。公立学校的规模将由它吸引的顾客的数目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当局划定的地理界限或分配学生数额来决定。凡建立非赢利性学校的家长(目前已有少数家长这样做了),政府都将确保他们得到教育经费。民间组织(从素食主义者团体到童子军以及基督教青年会)都可以建立学校并吸引顾客。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新型的私立学校将会崛起,开发广阔的新市场。
现在让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凭单计划可能带来的问题,以及人们已经对它提出的一些异议。
(1)宗教和政府问题。如果父母可以用凭单支付教会学校的学费,这是否违背了第一号修正案呢?不论这是否违背第一号修正案,重要的问题是:在中小学教育中采取一项加强宗教作用的政策是否合适呢?
最高法院对于各州资助家长送孩子上教会学校的法令一般都予以否决,尽管它还从来没有机会裁决一个既包括公立学校,又包括私立学校的成熟的凭单计划。但是,它今后很可能对这样一个计划作出裁决。很显然,最高法院采纳的计划将把与教会有关的学校排除在外,而适用于所有私立和公立学校。这样一种有限制的计划将远远胜过现行的制度,而且也不逊于一个毫无限制的计划。目前与教会有关系的学校可以通过把自己划分成两部分来达到政府所要求的条件:一部分与宗教无关,是独立的学校,可以接受凭单;另一部分带有宗教性质,主要组织课外活动和星期日活动,由家长或教会直接提供资金。
这种牵涉到宪法的问题只能由法院来解决。但是,要强调的是,领取凭单的是家长,而不是学校。根据美国军人法案,退伍军人可以自由选择罗马公教会学校或其他学校。而且据我们所知,迄今为止并没有人对此提出过第一号修正案的问题。社会保险金和福利津贴领取者可以随意在教会商店里购货,甚至可以把政府救济金捐献给教会,对此,也没有人提出过第一号修正案的问题。
无论律师和法官如何花言巧语地狡辩,我们确实认为,目前惩罚不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的家长的做法,违背了第一号修正案的精神。公立学校也在传授宗教,只不过不是信奉哪一个神的正式宗教,而是一整套价值观念和信仰,但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宗教。目前的做法剥夺了一些家长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们不相信公立学校传授的那种宗教,但却不得不为自己的子女接受这种宗教教育交纳学费,而要让孩子逃避这种宗教教育则必须花更多的钱。
(2)财政耗费。对凭单计划的第二条反对意见是,由于要为大约10%的目前正上教会学校或其他私立学校的孩子们提供凭单因而会增加纳税人为整个中小学教育所付的钱。其实,这只对那些忽视把孩子送到非公立学校的家长所受的歧视的人才成为“问题”。凭单计划的普遍实行将结束那种用税金来教育一部分儿童,而不管其他儿童的不平等现象。
不论怎么说,我们可以采用以下一种十分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使凭单金额大大低于每个公立学校学生的费用,以保持公共费用总额不变。在竞争性的私立学校上花少量的钱,很可能带来比现在在公立学校上花大量的钱更好的教学质量。这可以由教会学校每个学生的费用之低来说明。(名牌贵族学校收费高昂也不值得奇怪,正象1979年“二十一家俱乐部”对它的第二十一只汉堡包收费超过十二点二五美元一样,这并不意味着麦克唐纳饭店不能以四十五美分的高价出售汉堡包,或以一点零五美元的高价出售“大麦克”。)
(3)欺骗的可能性。谁能确保凭单用来给孩子交学费,而没有用来给爸爸买啤酒或给妈妈买衣服呢?我们的回答是应该把凭单的使用范围限制在已经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只允许在这类学校中将它兑换成现金。这不能防止所有欺骗行为(因为政府官员可能把它作为“酬金”送给家长),但是,它将把欺骗行为控制在一个可以容忍的范围内。
(4)种族问题。有一段时期,南方一些州为防止白人和黑人享有同等待遇而实施了凭单计划。这样做被判为非法的。防止公立学校在实行凭单计划时采取歧视做法也是非常容易的:政府将只兑换那些没有歧视行为的学校的凭单。研究凭单计划的学者遇到的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由于持有凭单的人可以自由选择学校,这就有可能增加校园内的种族隔离和阶级隔离,从而加剧种族冲突,而形成一个日益分裂和等级更加分明的社会。
我们认为,凭单计划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它会缓和种族冲突,促成一个黑人和白人为共同的目标而合作的社会,同时,又将互相尊重各自的权利和利益。许多人之所以反对强迫的种族合并,并不是出于种族主义情绪,而是因为他们多少有些担心孩子的人身安全和教学质量受到影响,这种担心也是很有理由的。如果种族合并不是靠强制,而是靠自由选择产生的话,那才是最成功的。非公立学校、教会学校和其他类型的学校,常常站在消灭种族隔离的前列。
一些公立学校发生暴力行动,仅仅是由于政府强迫人们上指定的学校造成的。只要给予学生足够的选择自由,无论是黑人学生还是白人学生,无论是穷人家出身的学生还是富人家出身的学生,无论是北方学生还是南方学生,都会离开那些不能维持纪律的学校。那些培养无线电和电视技术人员、打字员和秘书或无数其他专业人材的私立学校,很少发生纪律问题。
让其他学校象私立学校那样专业化,共同的利益就将战胜肤色的偏见,实现比目前更为广泛的种族平等。种族平等将成为现实,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凭单计划的实行,将废除为大多数黑人和白人共同反对的用校车接送学生的制度。也许人们还会用校车接送学生,而且接送的学生可能会更多,但这将是自觉自愿的,正象今天接送孩子上音乐课、舞蹈课那样。
黑人领袖不支持凭单计划的态度,是我们长期以来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他们的选民从凭单计划中得到最多的好处。这将给予他们控制子女上学受教育的权力,摆脱各级官僚机构的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摆脱教育机构的顽固控制。黑人领袖们通常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私立学校去读书,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帮助别人也这样做呢?我们怀疑这是因为凭单计划将使黑人摆脱其政治领袖的控制。这些领袖通常把教育的控制看作是获得政治支持和权力的来源。
【按:黑人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在《财富贫穷与政治》中也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
然而,由于向广大黑人群众的子女开放的教育机会日益减少,越来越多的黑人教育家、专栏作家和其他社会团体的领袖们已经开始支持凭单计划。争取种族平等会议已把支持凭单计划作为其主要的政策目标。
(5)经济等级问题。凭单计划将对社会和经济等级结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也许是研究该计划的人们分歧最大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公立学校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象是一个熔炉,使富人和穷人,本国人和外国人,黑人和白人能够融洽地生活在一起。这种情形在小社区内,过去和现在都是真的,但在大城市里,却几乎全然不是这样。在那里,由于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和收取的学费同所在地区关系很大,因而造成了居民的分化。所以毫不奇怪,国内大多数名牌公立学校都设在高收入居民区之中。
在凭单计划下,大多数儿童很可能仍将上附近的小学,而且就近入学的人数肯定要比现在多,因为该计划实施后将不再用校车强迫接送学生。但是,由于凭单计划将使各居民区的组成更加参差不齐,因而某一地区内的学校种类可能要比现在多得多。中等学校的等级几乎肯定要比现在少。侧重某一方面的学校,如艺术学校、理科学校或外语学校,将广泛地吸引来自各个不同居民区的学生。当然,自愿选择仍将严重地影响学生的阶级组成情况,但这种影响将比今天的小得多。
对于凭单计划,人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家长是否能够并乐意“添补”凭单金额。如果凭单金额为一千五百美元,家长可能另外添上五百美元,把孩子送到学费为两千美元的学校。但有人担心,由于广大中等和高等收入的家长愿意添补不足的学费,而收入低的家长拿不出钱,结果,凭单计划可能在提供教育机会上造成比现行制度更大的不平等。
这种担心致使一些支持凭单计划的人提议禁止“添补”。
孔斯和修格曼写道:
私人添补学费的自由,使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不能接受弗里德曼的计划。……无力添补学费的家庭将不得不去上那些凭单之外不再另收学费的学校,而比较富裕的家庭则可以自由地在学费高昂的学校中进行选择。今天全靠私人资金和个人财富进行的选择,明天将会变成一种由政府资助的、令人反感的特权。……这违背了一项基本的价值准则,即:任何提供选择自由的计划必须保证所有家庭的孩子享有同等的上某一所学校的机会。
弗里德曼的看法是:在一项允许添补学费的提供选择自由的计划下,穷困家庭的处境可能要比他们今天的处境强一些。然而,不论该计划将使这些家庭的教育得到多大改善,政府有意识地资助经济分离的做法,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弗里德曼的计划是政治上唯一可行的计划,那我们不会对它抱有多大热情。
对我们来说,这种观点似乎是前一章讨论的那种平等主义的一个例证:宁让父母把钱花在放纵的生活上,也不让他们把钱用在改善自己子女的教育上。这种观点在孔斯和修格曼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他们曾在另外的场合说过:“以牺牲个别的孩子的发展为代价的平等的许诺,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平等主义的最终腐败,不论其本质上有任何好的东西。”这是一种我们衷心赞同的情绪。但我们认为,从凭单计划中受益最大的是非常贫穷的人。一个人怎么能够避免“政府资助”所谓“经济分离”,就闭眼不看它“使穷人的教育得到了多大的改善”,而自以为是地为反对凭单计划的意见辩护呢?即使能够确实证明这种计划带来了某种程度的“经济分离”,也不能这样做,更何况这根本就不是事实呢。相反,通过大量的研究使我们相信,它将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另外,我们要指出的是:“经济分离”这个词的意思非常含糊不清,难以明白它所表达的确切含义。
平等主义对人们的影响是非常强烈的,以至赞成有限的凭单计划的人甚至不同意试一试无限制的凭单计划。但是,据我们所知,除了有人毫无事实根据地宣称无限制的凭单制度将导致“经济分离”外,再没有人提出过任何别的理由。
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是知识分子往往小看贫穷家长的又一证明。即使最穷的父母也能(而且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积蓄几个钱来改善子女的教育状况,尽管这笔钱不足以支付当前公共学校的全部学费。我们估计,穷人家庭也会象其他人家一样添补学费,尽管添补的数额可能较小。
如前面指出的,我们认为一项无限制的凭单计划将是改革现行教育制度的最有效的途径。这种教育制度非改革不可,因为正是这种制度注定了市内的许多孩子过贫穷悲惨的、行凶犯罪的生活。这项计划还将摧毁现行经济分离的大部分基础。在这里,我们无法提供这种见解的全部根据,但只要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早先的一个论断,就能显示我们的看法的合理性:在各经济集团所获得的各种商品和劳务(除防范犯罪行为的保护措施外)中,有比教育质量差别更大的东西吗?对各种不同经济集团开放的超级市场,是否象学校一样在质量上差异那么显著?凭单计划几乎丝毫不会改善为富人提供的教育的质量,却可以适当地改善为中产阶级提供的教育的质量,同时极大地改善为穷人提供的教育的质量。由此我们可以肯定,穷人得到的好处,将大于某些富人或中产阶级的家庭由于能够避免为孩子交纳双重学费而得到的好处。
(6)对新学校的怀疑。这是想入非非的计划吗?现在的私立学校几乎全是教会学校或纨袴子弟学校。凭单计划会不会是只补贴了这些学校,结果把大量的来自贫民窟的学生留在质量低劣的公立学校呢?有什么理由认为会出现新的学校呢?
理由就在于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市场。目前,市、州和联邦政府每年在中、小学上花费将近一千亿美元。这个数目比餐馆和酒吧间每年花在食品和酒上的钱多三分之一。后者为各阶层和各地区的人们开办了足够的各式各样的餐馆和酒吧间。前者或甚至它的一部分也一定能开办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学校。
凭单计划将开辟一个庞大的市场,吸引来自公立学校或其他职业的许多顾客。在同各类人谈论凭单计划时,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很多人都说,“我一直想去教书(或办一所学校),但我不能忍受教育机构的官僚主义、烦琐的办事程序和公立学校普遍的思想僵化。如果实施你的计划,我愿意试着办个学校。”
很多新学校将由非赢利组织来办,其他的则由赢利组织来办。对于未来学校工业的最终结构,现在尚无法预言。这将由竞争来决定。现在可以预言的是:只有那些能够满足顾客需要的学校才会生存下去,正如只有满足顾客需要的餐馆和酒吧间才能够生存下去一样。竞争将确保它们满足顾客的需要。
(7)对公立学校的影响。把管理学校的官僚的花言巧语同实际存在的问题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全国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联合会宣称,凭单计划将会断送公立学校体制,而按照他们的说法,公立学校体制是我国民主制度的根本和基石。但他们说这些话时,从来没有列举出事实证明:今天的公立学校体制取得了预想的结果——不管早先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这些组织的发言人也从来没有说明,为什么办得那样好的公立学校会害怕私立学校的竞争?如果公立学校办得不好,为什么要反对它“垮台”。
其实,对公立学校的威胁来自其自身的缺陷,而不是它们的成就。目前,在共同利益把人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小地方,公立学校,特别是公立小学,还是办得比较令人满意的,在这样的地方,即使是最全面的凭单计划也不会对公立学校产生多大影响。公立学校将继续保持其统治地位,或许由于潜在竞争的威胁,而使它有所改善呢。但是,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公立学校办得十分糟糕的城市贫民窟内,大多数家长无疑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私立学校去读书。
这将引起一些过渡性的困难。那些最关心子女幸福的家长很可能首先把孩子转到私立学校去。尽管他们的孩子并不比剩下的孩子更聪颖,但他们将受到更多地鼓励去念书并有着更有利的家庭支持。结果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一些公立学校只剩下一些“渣滓”,他们受到的教育从质量上来说可能比目前还要糟糕。
随着私人市场接管教育事业,整个教育质量将极其迅速地提高,以至最差的学校在绝对质量上也会有所改善,尽管相对水平还是低的。正如哈莱姆预备学校和其他类似的例子所表明的,在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情,而不是使人们互相仇视,和对一切都淡漠无情的学校,许多原来的“渣滓”学生在学校的表现都是非常好的。
正如亚当·斯密在二百年前所说的:
“讲授果真值得学生到堂倾听,无论何时举行,学生自会上堂,用不着校规强制。对于小儿……为要使他们获得这幼年时代必须取得的教育,在某种程度确有强制干涉之必要。但学生一到了十二、三岁以后,只要教师履行其职务,无论哪一部分的教育,都不必要加以强制的干涉。……
未有公立机构的那一部分教育,大抵教得最好,这是值得注意的。”
凭单计划的障碍
自从二十五年前我们首次把凭单计划作为解决公立学校制度缺陷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提出以来,支持在增加。今天,一些全国性组织也表示赞成。自1968年起,先是联邦经济机会办公室,而后是联邦教育委员会,相继鼓励和资助了对凭单计划的研究工作,并且表示愿意为这方面的试验提供资金。1978年,密执安州为通过一项有关凭单计划的修正案进行了投票。1979年,加利福尼亚州展开了一场运动,要求在1980年对凭单计划进行投票表决。最近,又成立了一个非赢利性的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凭单计划。在联邦一级,有人提出法案,打算对交付给私立学校的学费实行某种程度的免税,这些法案几次险些被通过。尽管它们本身并非凭单计划,但它们却是这种计划的部分翻版,这是由于免税额是有限度的,也由于这种方法很难把无力或有很少力量纳税的人都包括进去。
教育界官僚们的自私自利,表现在他们是反对在学校教育中推行市场竞争的主要障碍。正如埃德温·G.韦斯特教授所说,这个在美国和英国公共教育事业的建立中起过关键性作用的特殊利益集团,坚决反对研究、考察或试验凭单计划的所有尝试。
黑人教育家和心理学家肯尼思·B.克拉克总结了管理学校的官僚们的态度:
……看来,为提高城市公立学校工作效率的必要改革,并不会由于它应当到来而到来。……如想了解教育机构抗拒这种改革的能力,最要紧的是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公立学校制度是很少受到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竞争的,是受到保护的公有垄断集团。批评美国城市公立学校的人,甚至包括我这样严厉的批评者,几乎没有哪一个敢于对目前公立教育组织的现状提出疑问。……也不敢对选拔学监、校长和教师的标准和水平提出疑问,不敢问一问所有这一切给公立教育的目标——即培养从事民主事业的有知识和文化的,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尊严、创造性而又尊重他人的人——带来的影响。
垄断组织根本不必关心这些问题。只要各地的公立学校可以确保得到州政府的补助和联邦政府越来越多的补助,只要它们不必为激烈的竞争节省开支,指望公立学校的效率有所提高的一切想法就是痴心妄想。如果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现行的教育制度——不包括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因为它们的发展几乎已经到头了——那么,改进公立教育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
这一估计的正确性后来被教育机构对联邦政府出资进行凭单计划的试验的反应所证实。当时许多地区主动制定了颇有成功希望的计划。但只有加利福尼亚州阿卢姆罗克一个地方的计划,经过艰苦磨难,获得了成功。我们根据亲身经历了解得最清楚的例子发生在新罕布什尔州。当时该州的教育委员会主席威廉·P.比特本德进行了一项试验。条件似乎满好,联邦政府拨了款,定出了详细计划,选出了作试验的一些地区、家长和行政管理人员也达成了初步协议。正当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当地学校的学监和其他头头却劝说一个又一个地区退出了预定的试验,结果,整个探索夭折了。
阿卢姆罗克的试验是实际进行的唯一试验,但很难说它是真正的试验。试验仅仅限于几所公立学校,而且除政府拨款外不允许家长或其他人捐款。一些所谓的小型学校建了起来,它们的课程各不相同,家长可以任选一所学校让孩子在那里上三年学。
正如负责这项试验的唐·艾尔斯所说:“所发生的意义最为重大的事情是:教师第一次有了一些权力。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安排适合学生需要的课程。州和地方学校委员会对麦卡科兰学校的课程安排不予干涉。家长越来越多地参与学校的事情,更经常地参加学校的会议。另外,如果他们看中了另一所学校,他们有权让孩子转学。”
尽管这项试验的范围有限,但由于家长可以进行更多的选择,因而对教育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考试分数上看,麦卡科兰学校从所在地区的第十三名上升为第二名。
但是,现在这项试验已经成为一件过去的事了。象哈莱姆预备学校的命运一样,教育机构断送了它。
在英国也有同样的阻力。英国的一个叫做“选区教育凭单试验之友”的非常有力量的组织,在英格兰的肯特郡的一个小镇上进行了四年的努力来推行一项试验。政府当局表示赞同,然而教育机构却极力反对。
职业教育者对凭单计划的态度,可以从丹尼斯·吉所说的话中清楚地看出来。此人是肯特郡阿什福一所学校的校长兼当地教师协会秘书,他说:“我们把这项计划看成是我们与家长之间的一道障碍。他们拿着小纸片(即凭单)来找你,指使你干这干那。我们之所以要对一些事情作出判断,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样做对每个孩子最有利,而不是因为有人说:‘要是你们不干,我们就自己干。’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市场上的那种生意经。”
换句话说,吉先生反对让顾客(在这里指家长)决定自己的子女应受什么教育,而想让官僚们来决定。
吉先生说:
“我们通过管理机关向家长负责;通过检查人员向肯特郡议会负责;通过女王的检查官向国务大臣负责。这些人是能够作出正确判断的内行和专家。”
“我不能肯定家长都知道什么样的教育对他们的孩子最有利。他们知道给孩子吃什么最好,知道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对孩子最有益。但我们学的却是弄清孩子们身上存在的问题,发现他们的弱点,纠正那些需要纠正的毛病。我们希望在家长的协助下,而不是在不正当的压力下,自由地干这些事。”
不消说,至少有一部分家长是对此持不同看法的。住在肯特郡的一位电工和他的妻子为使他们的儿子上一所他们认为最适合于他的学校,竟与官僚们斗争了一年的时间。
莫里斯·沃尔顿说:
“我认为,在现行教育制度下,当家长的没有一点选择的自由。他们要由教师来告诉怎样做才最有利。他们被告知说,教师们正在从事伟大的工作,对此不要多加过问,如果实行凭单计划的话,我认为它将使教师和家长结合在一起,使他们的关系密切起来。为自己的子女感到担忧的家长,会把自己的孩子从办得不好的学校转到办得好的学校去。……如果一所学校一无是处,存在着破坏公共财产的现象,而且纪律非常松弛,学生无法念书,那它会因此而垮台,在我看来,这倒是件好事。
“眼下,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教师把它当作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但同时又用它作紧箍咒套在家长们的头上。家长找到教师说,我对你们的教学不满意。但教师会相当粗暴地回答说,你不能把孩子带走,也不能给他转学,你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走开,别来麻烦我。这可能是今天某些教师新采取的态度,而且他们确实常常这样对待家长。但是,现在(有了凭单计划以后),他们的地位颠倒过来了,只有家长们能大声大气地对教师讲话:让他们卖力气干活,让家长的钱花得上算,能够更多地参与学校事务。”
尽管教育机构坚决反对,但我们相信,凭单计划或其他类似的计划将很快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被采纳。我们对教育事业要比对福利事业更乐观,因为教育同我们许多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比起消灭救济金分配上的浪费和不公平来说,我们愿意尽更大的努力来改善孩子们的教育状况。对教育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就我们来看,目前减少这种不满情绪的唯一途径是使家长有更大的选择。这是切实可行的措施。尽管凭单计划一直受到抵制,然而,却一再被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提出来。
高等教育的症结
同初等和中等教育一样,今天存在于美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也是双重的:既有质量问题,又有平等问题。在这两个方面,由于没有强迫入学制而使问题大为改观。法律没有规定某人必须上大学,因此,对有志继续受教育的学生来说,在上哪所大学方面,他们可以进行广泛的选择。广泛的选择减轻了质量问题,但加剧了平等问题。
质量:由于没有人违背自己的意志(或其家长的意愿)上一所学院或大学,因此,任何一所大学要想办下去,就得满足学生的最低要求。
这里存在着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在收学费低的官办学校,学生是二等顾客。他们是部分靠纳税者花钱资助的慈善事业的施舍对象。这一特征影响到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
收学费低的事实意味着,市立和州立的高等学校除了吸引许多想接受教育的、用功的学生外,还吸引了许多其他男女青年,他们来这里是因为学费低,有住宿和伙食补贴,能同其他年青人在一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只不过是高中毕业但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时的一段令人愉快的歇息期。上课、考试和取得毕业分数并不是他们来上学的主要理由,而是他们为获得其他好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由此而带来的一个结果是退学率很高。例如,在国内公认的最好的州立大学之一,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中,被录取的学生中大约只有一半人完成整个大学的学业,而这在官办大学中,毕业的比率还算是高的呢。当然,有些学生退学后又转上了其他学校,但这只对退学总人数产生很小的影响。
另一结果是,课堂上的气氛往往使人感到压抑,而不能激发学习的热情。当然,各学校的情况并非千篇一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课程和教师。各个学校内用功的学生和尽职的教师总可以想办法凑到一起,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同上述情况一样,这只能对所浪费的时间和税款起很小的补偿作用。
在市立和州立大学中,不仅有勤奋的学生,而且有优秀的教师。但是,在有名望的官办学校中,对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的酬劳办法是不利于那里的教学的。教师们靠研究和出版成果来提升,管理人员靠从州立法机关那里争取到更多的拨款来擢升。结果,甚至最有名的州立大学,如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的威斯康星大学或密执安大学并不以其教学质量闻名。它们是以培养研究生的工作、科研工作和体育运动队而出名的,这才是给它们带来好处的地方。
私立大学的情况颇不相同。这些学校的学生需要付很高的学费,即使学费支付不了大部分教育费,也可以支付相当一部分教育费。所交学费来自家长、学生自己挣的钱、政府贷款以及奖学金。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学生成了一等顾客;他们为得到的教育而付钱,因而他们想要得到与他们所付的钱价值相等的教育。
学校出售教育,学生购买它。同在大多数自由市场上的情形一样,买卖双方都受到强烈刺激来为对方服务。如果某一大学不能提供学生所指望的那种教育,他们就会上别的大学。学生想得到他们所付学费的全部价值。正如一位在颇负盛名的私立大学达特默思学院上学的学生所说:“当你想到修一门课程要花三十五美元,而又考虑到用这三十五美元能干其他事情时,你肯定会专心致志地听课。”
一个结果是,上私立大学的学生完成大学学业的人数,大大多于公立大学完成大学学业的人数。达特默思学院的毕业率为95%,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毕业率仅为50%。达特默思学院的比率在私立大学中可能是较高的,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比率在官办大学中也是较高的一样。尽管如此,它们之间的差距也还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样来谈论私立院校是过于简单了。除教育外,它们还出售另外两种产品:纪念物和研究工作。个人和基金会捐赠了私立院校的大部分建筑和教学设备,资助了教授职位和奖学金。大部分研究经费来自捐赠、联邦政府的特别拨款或其他来源。捐赠者出钱,是因为他们想促进某件他们认为值得促进的事情;另外,以个人命名的建筑、教授职位、奖学金也可以纪念某位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它们称为纪念物的原因。
出售教育和出售纪念物能够结合在一起,说明自愿合作具有被人们大大低估了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通过市场的作用可以利用人们自私自利的动机来为广泛的社会目标服务。亨利·M·莱文在谈到高等教育的筹资问题时写到:“人们怀疑:这个市场是否会资助古典文学系或其他许多人文学科方面的教学计划。这方面的教学活动可以促进文化知识的发展,而人们普遍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文化知识的发展将广泛地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使这些活动维持下去的唯一途径是靠直接的社会补贴。”这里的所谓补贴指的是政府拨款。莱文先生显然是搞错了。广义上的市场,一直维持着私人机构的社会活动。正因为这些活动对整个社会有益,而不是只为捐赠人的眼前私利服务,才使得它们对捐赠人具有吸引力。假设某某太太想为其丈夫某某先生增添荣誉,那么,她或别人是否会认为只要让某一大型工业企业(这可能是这位先生的真正纪念物和对社会福利事业的真正贡献)用这位先生的名字命名一座新建的工厂就行了呢?他们显然不会这样认为。另一方面,如果这位太太出资帮助一所大学修建一座以其丈夫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或建筑物,或资助以其丈夫的名字命名的教授职位或奖学金,那就会真正被认为是对其丈夫的赞颂。它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确实提供了一项社会服务。
学生们以两种方式参加制造教学、纪念物和研究工作的合资企业。他们既是顾客,又是雇工。他们靠促进纪念物和研究成果的出售,为教学基金作出贡献,从而获得他们的一部分教育。这是说明自愿合作的途径和潜力是多么复杂而又难以捉摸的另一个例子。
许多名义上官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实是一种混合体。它们收学费,从而把教学卖给学生。它们接受盖建筑物的捐赠,从而出售纪念物。它们同政府机构或私人企业签订研究合同。很多州立大学得到大量的私人捐赠,如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密执安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这些只是其中的少数几个。我们的印象是:一般来说,市场的作用越大,学校的教学也就搞得越好。
平等。使用税款来资助高等教育的理由通常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莱文先生在上面提出来的:高等教育除了给学生本身带来好处外,还产生“社会福利”。第二个理由是说,为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需要政府的资助。
(1)社会福利。当初我们第一次论述高等教育时,我们对第一种理由是抱有极大同情的。现在则不然了。从那时到现在,我们一直力图引导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搞清楚他们所说的“社会福利”到底指的是什么。然而,得到的回答几乎总是很差劲儿的经济学概念。我们被告诉说,国家可以因为拥有更多的掌握高超技术和受过良好训练的人而得到好处;为得到这种技术水平而进行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更多的受过训练的人可以提高其他人的生产率。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但是,没有一条可以成为补贴高等教育的正当理由。这些说法也同样适用于有形资本(即机器、厂房等),但是,没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用税款来补贴通用汽车公司或通用电器公司的资本投资。如果高等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经济生产率,那么人们可以通过收入的提高获得由此而产生的好处,因而个人的私利刺激人们去接受高等教育。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无形的手会使人们的个人利益服务于社会利益。靠补贴教育来改变他们的个人利益的做法本身违背了社会利益。那些只愿意上有补助的学校的多余的学生,恰恰是那些认为得到的好处低于所付的学费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会愿意自己付学费了。
偶尔得到的回答是很好的经济学概念,但它们所依据的常常是武断的假设而不是有根有据的事实。最近的一个例子见于由卡内基基金会建立的高等教育专门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在最后的一份题为《高等教育:谁付钱?谁受益?谁应该出钱?》的报告中,该委员会对所谓的“社会福利”作了总结。该报告中包括上面一段讨论过的不恰当的经济论据——也就是说,它把受教育的人得到的自然增长的福利,当成是第三者得到的福利。但是,它也列举了一些所谓的好处。如果这些好处确实存在的话,它们将增加那些并非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福利,由此而可能证明政府补贴高等教育是有道理的。它列举的好处有:“知识的总进步……;民主社会的更大的政治效能……;由个人和集团之间更好的了解和相互谅解所取得的更大的社会效能;对文化遗产更有效的保护和发展。”
卡内基委员会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至少对可能产生的“高等教育的不良后果”在口头上谈了谈,尽管所列举的例子只是“由当前多余的博士学位(这不是社会,而是个人造成的)所引起的个人的失败情绪和在过去由于校园里爆发的混乱而引起的公众的不悦。”读者应注意,他们列举的好处和“消极后果”,经过多么仔细的选择,带有多么深的偏见。在印度那样的国家,大批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成了社会和政治极度不稳定的根源。而在美国,“公众的不悦”几乎算不上是“校园混乱”所带来的唯一的或主要的消极后果。更为重要的后果是对大学的管理、对“民主社会的政治效能”,以及对“通过……更好的了解和相互谅解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产生的有害影响,而这些都是该委员会毫无保留地列举出来的高等教育给社会带来的好处。
该报告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它认识到,“即使没有政府补贴,高等教育给社会带来的某些好处也会作为私立教育的副作用而出现。”然而,这也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尽管该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的很费钱的专门研究,但是,它并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态度去鉴别各种所谓的社会效果,没有从量的方面粗略地估计它们的重要意义,也没有粗略地估计一下。如果政府不提供补贴会产生多少社会效果。结果,它提不出任何证据,来说明总的社会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更不必说能够充分证明花在高等教育上的数十亿美元的税款是否取得了任何真正的积极效果。
该委员会满足于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没有任何精确的——甚或不精确的——方法能够估计出个人和社会从个人和政府开支中得到了多少好处。”然而,这并不妨碍它坚决地、毫不含糊地建议增加早已是非常庞大了的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补贴。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特殊要求。卡内基委员会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前校长克拉克·科尔领导。在包括科尔在内的由十八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中,有九人现在担任或曾经担任过高等学府的校长,另外五名成员任职于与高等教育机构有关的部门。剩下的四人曾在大学的董事会或评议会里干过事。当工商业者高举着自由企业的旗帜,呼吁得到关税、定额或其他方面的优惠向华盛顿进军时,学术界会很容易地看出这是一种特殊要求,从而对之加以嘲笑。如果一个钢铁工业委员会有十八名成员,其中十四名来自钢铁工业,而它建议增加政府给予钢铁工业的补贴,学术界又会说些什么呢?我们至今还未听到学术界对卡内基委员会的建议发表过任何意见。
(2)教育机会的均等。促进“教育机会均等”是通常为使用税款资助高等教育辩护的主要理由。用卡内基委员会的话来说,“为了使教育机会尽可能地均等,我们赞成让公众暂时为教育多掏一些钱。”用卡内基基金会的话来说,“高等教育是通向更广泛的机会均等的主要途径。它越来越为出身贫寒的人、妇女和少数民族所拥护。”
这一目标是可嘉的,事实的叙述也是正确的。但是,它们之间缺少一个中间环节。政府的补贴是促进了还是阻挠了目标的实现?高等教育是否由于有了政府补贴才成为“通向更广泛的机会均等的主要途径”,还是没有这种补贴也能促进机会均等呢?
卡内基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的一组简单统计数字说明了问题:1971年入私立大学的学生中,20%来自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17%来自收入在五千——一万美元之间的家庭;25%来自收入超过一万美元的家庭。换句话说,私立大学为来自家庭收入最低和最高的青年男女提供了比官办大学更多的机会。
而这仅仅是冰山之巅。来自中等和上等收入家庭的青年上学的人数为来自低收入家庭青年的二倍或三倍,而且,他们往往上收费较高、学制较长的大学(他们通常上四年制的专科或本科学校,而不上两年制的初级大学)。结果,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从政府补贴中受益最多。
【作者按:卡内基委员会:《高等教育》,第176页。书中的数字不是根据卡内基委员会制作的表格计算的,而是根据该委员会引用的资料来源:美国1971年国情普查报告P-20,第241号,第40页,表140我们在计算时发现卡内基报告中的数字有些小错误。我们给出的数字多少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与配偶住在一起的已婚学生是按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配偶的家庭的收入归类,而不是按他们父母的收入归类。如果除开已婚学生,数字会更大: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的孩子有22%上私立学校,收入在五千至一万美元之间的家庭为17%,收人高于一万美元的家庭为25%。根据美国国情普查局的数字,在1971年在校的十八至三十四岁之间的公立院校学生当中,来自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的学生不到14%,虽然在这一年龄组,22%以上的人来自这些低收入家庭。57%的公立院校学生来自收入高于一万美元。】
一些出身贫穷的青年确实从政府补贴中得到了好处。一般说来,他们是穷人中生活境况较好的人。他们具有的天赋才能和技能使他们能从高等教育中受益,这种技能甚至能使他们用不着上大学就能挣到较高的工资。不论怎样,他们注定要成为穷人中境况好的人。
这里有两份详细的研究报告,一份是关于佛罗里达州的,另一份是关干加利福尼亚州的,它们说明了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从面向低收入阶层转向高收入阶层的程度。
佛罗里达州的研究报告把四个收入阶层中的每个阶层在1967-1968年度中从政府高等教育经费中得到的全部好处与他们以纳税形式所花的钱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只有最高收入阶层得到了净收益,这个阶层得到的好处比他们付的钱多60%。最下面的两个阶层付的钱比他们得到的好处多40%;中等阶层付的钱比他们得到的好处多20%以上。
1964年关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研究报告,也得出了令人吃惊的重要结论,不过表达方式稍有不同,它所比较的是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和没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得到了相当于他们平均收入1.5-6.6%的纯收益,得好处最多的是那些有孩子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念书而且平均收入最高的家庭。没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平均收入最低,而且还要从他们的收入中拿出8.2%资助高等教育。
事实是不容置疑的。甚至卡内基委员会也承认,高等教育经费的再分配产生了违反政府意愿的结果,不过,人们必须非常仔细地阅读卡内基委员会的各份报告,才能在下面这样的话语中发现他们的这种态度:“一般说来,这一‘中等阶层’……得到的公共补贴是相当可观的。通过补贴的合理的再分配,我们可以达到更大的公平。”该委员会提出的主要对策还是老一套:进一步增加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开支。
就我们所知,似乎没有比政府资助高等教育更为不平等的政府计划了,也没有哪一项计划能更清楚地说明“董事规则”。我们这些中等收入和高等收入阶层的人们,诱骗穷人大规模地补贴我们,然而,我们不仅丝毫不感到耻辱,反而大吹大擂我们的大公无私精神。
【按:这里有个表格,对内容没有太大影响,故删去。】
高等教育:解决办法
每个男女青年,无论其父母收入、社会地位、居住地区或种族怎样不同,只要愿意现在交付学费或愿意毕业后用挣得的较高工资来补交学费,都应得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为确保所有的人都有上学的机会,有充足的理由提供足够的贷款,有充足的理由传播有关这种贷款的消息。并敦促经济情况较差的人们去利用这一机会。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让那些没有享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为享受高等教育的人掏腰包。如果是政府经管高等教育机构,它收取的学费应该相当于向学生提供的教育和其他服务的全部费用。
虽然确实应该废除纳税人为高等教育出钱的做法,但目前这在政治上似乎是办不到的。为此,我们将附带论述一项代替政府出资的、不那么激烈的改革方案——高等教育凭单计划。
代替政府出资的办法。由于大学生毕业后收入的差别很大,因此,以固定金额的贷款资助上大学的青年是有缺陷的。有些人干得很好,偿还贷款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有些人最终只能挣得有限的收入,偿还贷款对他们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在教育上花钱就是对一个有风险的企业进行投资,也可以说是对一个新建立的小企业进行投资。资助这种企业的最佳方法不是提供固定数额的贷款,而是对其股本进行投资,即“买进”某企业的股票,将来按股分红。
对于教育来说,就是“买进”某人未来的一部分收入,也就是说,如果某人同意在未来的工资中拿出一规定部分还给投资人,投资人就预付给他上学所需要的资金。采用这种方法,投资人可以从比较成功的人那里收回多于他当初投资的钱,从而补偿在那些不成功者身上投资损失的钱。按这种方式签定个人合同虽然在法律上似乎没有障碍,但这种方法并没有被人们普遍采用,我们猜测,其主要原因是这种合同的期限很长,实施起来费用高,困难多。
二十五年前(1955年),我们提出过一项计划,建议通过某一政府机构对高等教育进行所谓“资本投资式的”资助。该机构可以向任何符合最低质量标准的个人提供或帮助他们筹集上学所用的资金。它将在规定的年限内每年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条件是所提供的资金必须用于在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高等院校接受教育。反过来,个人将同意从他未来的超过一定数额的收入中,提取一定的百分比,偿还他从政府那里得到的资金。偿还给政府的钱可以很容易地与所交纳的所得税结合在一起,因而额外牵涉到的行政管理费是非常少的。偿债基额应与未受高等教育的人的平均收入相等;每年应偿还的数额要加以仔细的计算,以使整个方案能自给自足。这样,实际上使入学者负担了全部学费,投资金额就可以由个人的选择来决定了。
最近(1967年),一个专门研究小组建议实施一项与我们的计划相类似的计划,其名称很吸引人,叫做“教育机会银行”。该小组是约翰逊总统下令成立的,组长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杰罗尔德·R·扎卡赖亚斯教授。它对这项计划的可行性和为使其能够自足自助所需要的费用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该计划遭到了“州立普通大学及农业大学联合会”的猛烈攻击,想必本书读者是不会对此感到奇怪的。这正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私自利的谬说”的一个极好例证。
1970年,卡内基委员会提出了资助高等教育的十三条建议,其中第十三条提议建立一所“全国学生信贷银行”。该银行将提供长期贷款,偿还条件将部分地取决于届时的收入情况。该委员会说:“……我们认为,全国学生信贷银行不同于教育机会银行,它为学生提供补助金,而不是全部教育费用。”
最近,包括耶鲁大学在内的一些大学,研究或采纳了一些由它们自己管理的、偿还条件暂且不定的计划。由此可见,这种计划还是有活力的。
高等教育凭单计划。在用税款补贴高等教育的情况下,弊端最少的补贴方法就是前面谈到的在中小学采用的凭单计划。
让所有官办学校根据所提供的教育服务的全部费用来收学费,从而在平等的条件下与非官办学校竞争。用每年希望得到补贴的学生的人数除以每年用于高等教育的全部税款,所得的数目便是每一张凭单的金额。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选择在任何教育机构使用凭单,唯一的条件是他们所上的学校是需要补贴的学校。如果申请得到凭单的学生人数超过现有凭单的数目,就以最能为社会所接受的标准来分配凭单,如根据考试测验的成绩、体育才能、家庭收入或其他各种各样可能的标准来分配。由此可见,这种方法大致上与美国军人法向退伍军人提供教育的做法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军人法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所有退伍军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正如我们第一次提出这项计划时写道的:
采取这种方法,将更有效地促使各类学校之间开展竞争,更有效地利用它们的资源。它将消除要政府直接资助私立院校的压力。这样,一方面将使私立院校相对于州立院校获得发展,同时又使它们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和多样性。作为附带的好处,它还会起到严格控制补贴的作用。这种补贴教育机构而不是补贴人的做法,最终将导致不加区别地补贴所有大专院校的活动,而不是仅仅补贴各州认为应该补贴的活动。即使作一粗略的考察也可看出,尽管这两种活动有相互重叠的地方,但决不是一码事。
为促进公平而采用凭单计划的理由……是很明显的。……例如,俄亥俄州对本州公民说:“如果你们有小孩想上大学的话,我们将连续四年向他们主动提供丰厚的奖学金,只要他们能够满足起码的入学条件,并明智地选择上俄亥俄大学(或其他一些由本州政府资助的大学)。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想上(或你想让他们上)奥柏林学院或西部储备大学,那他一个钱也甭想得到,更不要说去上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西北大学、贝洛伊特大学或芝加哥大学了。”我们怎么能为这样一种方案辩护呢?如果把俄亥俄州打算花在高等教育上的钱花在所有高等院校的奖学金上,并要俄亥俄大学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其他院校竞争,难道不是更为公平,更能提高奖学金的水平吗?
自从我们最先提出这一建议以来,一些州相继有限度地实施了这方面的计划,颁发了可以在私立院校使用的奖学金,尽管只限于本州内的私立大学。另一方面,虽然纽约州立大学的董事会也根据同样精神制定了一项非常出色的奖学金计划,但这个计划却被该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一项宏伟计划代替了。洛克菲勒计划是要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样式办纽约州立大学。
高等教育方面的另一重要事态发展是联邦政府在资助高等教育方面的作用大大增大了,尤其是对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管理更多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干预是联邦政府活动大规模扩张的一部分。而联邦政府活动是在争取更大的民权的名义下采取的所谓“积极行动”。这种干预引起了高等院校教职员工的极大关注,他们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官员过多地干预教育。
这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遗憾的是高等教育的前途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威胁。学术界曾极力鼓吹对其他部门进行干预,只有干预到他们头上时,他们才感觉到干预带来的种种弊病:耗资巨大,学校的基本教学任务受到干扰,以及适得其反的效果等。此时,他们成了当初信仰的牺牲者,成了继续从私利出发仰给于联邦政府的牺牲者。
结论
按通常的习惯,我们把“受教育”和“上学”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但是,区别这两个词的意思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事物的本质。如果较为细心地使用这两个词的话,就会发现:“受教育”并不一定都得“上学”,“上学”也并不都“受到了教育”。许多学历很高的人并没有受到教育,而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并没有上过学。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我国的创建者当中是一位真正受过教育的、博学多才的人,然而,他只上过三、四年正规学校。这种例子举不胜举。毫无疑问,每个读者都认识一些学历很高,但他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认识一些没有上过学,但他认为很有学问的人。
我们认为,政府在资助和管理学校方面作用的不断加大,不仅导致了纳税人金钱的巨大浪费,而且导致了比自愿合作继续起较大作用所能产生的教育制度远为落后的制度。
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再没有比学校更令人不满意的机构了,几乎没有比它更能引起不满情绪,更能破坏我们的自由了。教育机构极力捍卫其现有的权力和特权。它得到了许多具有集体主义观点、热心公共事业的人们的支持。但它也受到了攻击。学生考试成绩普遍下降;城市学校中犯罪行为、暴力行动和秩序混乱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绝大多数白人和黑人起来反对用校车接送学生上学;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严密控制下,许多大专院校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感到惶惶不安,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教育事业中权力日益集中、官僚主义日益严重和社会化日益增强等趋势的严厉批判。
在这一章里,我们曾试图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采用凭单制度,该制度将给予不同收入的家长以选择子女所上学校的自由;在高等教育中采用贷款资助制度,偿还条件根据学生毕业后的收入情况来确定,该制度不仅将使教育机会均等,而且将消除目前征穷人的税来资助富人家子弟上学的不合理现象;或者,在高等教育中也采用凭单计划,该计划将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同时促使补贴高等教育的税款的分配更加公平。
【按:宋代朱子等人的教育实践及范式义庄的存在也能表明这种类型的教育制度符合儒家教育理念。】
这些计划是富有想象力的,然而,并非是行不通的。阻碍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和偏见,计划的实施和管理根本不成问题。在我国和其他国家,早已有人小规模地实施过类似的计划。公众是采取支持态度的。
这些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只要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或在目标不变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方法,我们就能够巩固我们自由的基础,并使教育机会的均等具有更为实在的意义。
本节内容概述
由于教师和家长可以自由选择如何教育孩子的方法。私人资金代替了税款,官僚手中的控制权被夺走,归还给了应该掌握控制权的人。
一种既能保证父母享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又能保持现有的财政来源的简单、可行的方法是实行及教育券计划。
教育券计划所体现的原则正好同退伍军人领取教育津贴的原则一样。退伍军人可以得到一张只能用于教育的凭单。他可以拿这份钱随便挑选学校,只要这所学校符合政府所规定的某些标准。
家长也应被允许在任何一个愿意接受他的子女的学校使用凭单,不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也不论是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城市或州,还是在其他地区、城市或州。这样,不仅将给每位家长较多的选择机会,同时也迫使公立学校通过收学费而自筹资金(如果凭单金额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完全自筹资金;如果不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部分地自筹资金)。这样,不仅公立学校之间要展开竞争,而且还要同私立学校竞争。
这个计划并不减少任何人为教育纳税的负担。它只是在社会有责任向孩子们提供教育的前提下,给予家长较为广泛的选择余地,让他们自己决定孩子应受什么样的教育。这个计划也不会影响目前为私立学校规定的标准,这些标准是为实施强迫入学法而制定的。
领取教育券的是家长,而不是学校。根据美国军人法案,退伍军人可以自由选择天主教学校或其他学校。
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采用教育券制度,该制度将给予不同收入的家长以选择子女所上学校的自由;在高等教育中采用贷款资助制度,偿还条件根据学生毕业后的收入情况来确定,该制度不仅将使教育机会均等,而且将消除目前征穷人的税来资助富人家子弟上学的不合理现象;或者,在高等教育中也采用教育券计划,该计划将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同时促使补贴高等教育的税款的分配更加公平。
下面的术可供参考:
和国内外顶级高校合作录制教学视频、实行网络教育、普及优质教育资源
国民建言形成各行业的路线图提供参考
组建巨型在线图书馆方便国民阅读
建设大型题库
官方出面购买国外大型论文库
作为教育家,柳诒徵爱才、重才,言传身教,培植弟子,“多能卓然而立”,人称“柳门成荫”。更多的人则是受到柳氏学问、道德、人格、理想的影响。在中国学术界,有说他“培养出来的文、史、地、哲各门乃至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最多”。柳氏教学之法,郑鹤声曾说,“柳先生的教学方法,以探求书本为原则。他讲中国史的时候,并不编辑课文,或某种纲要,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而指定若干惨考书籍,要我们自动地去阅读...,读了以后,要把心得记在笔记本上,由他详细批阅...他要学生平时以阅读正史(二十四史)为主,并经常从正史中出许多研究题目,要我们搜集材料,练习撰作能力,由他评定甲乙,当为作业成绩...这种治学方式,的确是很基本的,促使我们养成一种严谨笃实的学风,使我们一生受用不尽” ;张世禄回忆说他教导学生要能做“比较思考”,鼓励学生“自己找问题去钻研历史”;胡焕庸回忆他的授课“夹叙夹议,...既不是枯燥无味的考证,也没有不着边际的空谈,真可说是广征博引,有引人入胜之功”;茅以升曾说,“我从先生受业八年,感到最大获益之处,是在治学方法上从勤从严,持之以恒”。
教育思想方面,柳诒徵倡导自由教学,认为应当根本改革工厂批量生产式、机械式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以利于每一个人学生自由学习、个性发展。必修课程、标准以及教师资格可由教育部统一制定;国家组织严格的考试,各门课程及格者,授予相应文凭。学生自小学毕业后,听其自由求师。学堂停办,教师可自由授徒。同时,国家在各省市县设立公共的科学仪器馆、图书馆及各类音乐美术体育设施,适当收费或免费供学生使用。
附录《礼记·大学》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戮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附录《礼记·学记》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眾;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今之教者,呻其占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發然後禁,則捍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學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附录《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
今天所讲的问题,是怎么样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我们想研究一个什么方法,去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便不要忘却我前几次所讲的话,我们民族现在究竟是处于什么地位呢?我们民族和国家在现在世界中究竟是什么情形呢?一般很有思想的人所谓先知先觉者,以为中国现在是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但是照我前次的研究,中国现在不止是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依殖民地的情形讲,比方安南是法国的殖民地,高丽是日本的殖民地,中国既是半殖民地,和安南高丽比较起来,中国的地位似乎要高一点,因为高丽安南已经成了完全的殖民地;到底中国现在的地位,和高丽安南比较起来,究竟是怎么样呢?照我的研究,中国现在还不能够到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比较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更低一级,所以我创一个新名词,说中国是“次殖民地”,这就是中国现在的地位。这种理论,我前次已经讲得很透彻了,今天不必再讲。
至于中国古时在世界中是处于什么地位呢?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像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中的独强。我们祖宗从前已经达到了那个地位,说到现在还不如殖民地,为什么从前的地位有那么高,到了现在便一落千丈了呢?此中最大的原因,我从前已经讲过了,就是由于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国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我们想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我们知道现在是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既然知道了处于很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像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所以能知与合群,便是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大家先知道了这个方法的更要去推广,宣传到全国的四万万人,令人人都要知道;到了人人都知道了,那么我们从前失去的民族精神,便可以恢复起来。从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著觉,现在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唤醒起来,醒了之后,才可以恢复民族主义;到民族主义恢复了之后,我们便可以进一步去研究怎么样才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
中国从前能够达到很强盛的地位,不是一个原因做成的。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亚洲古时最强盛的民族,莫过于元朝的蒙古人。蒙古人在东边灭了中国,在西边又征服欧洲;中国历代最强盛的时代,国力都不能够越过里海的西岸,袛能够到里海之东,故中国最强盛的时候,国力都不能达到欧洲;元朝的时候,全欧洲几乎被蒙古人吞并,比起中国最强盛的时候,还要强盛得多。但是元朝的地位,没有维持很久;从前中国各代的国力,虽然比不上元朝,但是国家的地位,各代都能够长久;推究当中的原因,就是元朝的道德,不及中国其馀各代的道德那样高尚。从前中国民族的道德因为比外国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国到外来的蒙古人,后来蒙古人还是被中国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国到外来的满洲人,后来满洲人也是被中国人所同化。因为我们中国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此刻中国正是新旧潮流相冲突的时候,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
前几天我到乡下进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后进的一间厅堂去休息,看见右边有一个孝字,左边便一无所有,我想从前必定有一个忠字。像这些景象,我看见了的不止一次,有许多祠堂或家庙,都是一样的。不过我前天所看见的孝字,是特别的大,左边所拆去的痕迹还是很新鲜。推究那个拆去的行为,不知道是乡下人自己做的,或者是我们所驻的兵士做的。但是我从前看到许多祠堂庙宇没有驻过兵,都把忠字拆去了,由此便可见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他拆去。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民是可不可以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以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有所不惜,这便是忠。所以古人讲忠字,推到极点便是一死。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便不讲忠字,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便是大错。现在人人都说到了民国,什么道德都破坏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
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才自然可以强盛。
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对于仁爱,究竟是怎么样实行,便可以知道了。中外交通之后,一般人便以为中国人所讲的仁爱,不及外国人;因为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开办医院,来教育中国人救济中国人,都是为实行仁爱的。照这样实行一方面讲起来,仁爱的好道德,中国现在似乎远不如外国;中国所以不如的原故,不过是中国人对于仁爱没有外国人那样实行,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袛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
讲到信义,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义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在商业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袛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比方外国人和中国人订一批货,彼此不必立合同;袛要记入账簿,便算了事。但是中国人和外国人订一批货,彼此便要立很详细的合同;如果在没有律师和没有外交官的地方,外国人也有学中国人一样袛记入帐簿便算了事的,不过这种例子很少,普通都是要立合同。逢著没有立合同的时候,彼此定了货到交货的时候,如果货物的价格太贱,还要去买那一批货,自然要亏本;譬如定货的时候,那批货价订明是一万元,在交货的时候,袛值五千元,若是收受那批货,便要损失五千元;推到当初订货的时候,没有合同,中国人本来把所定的货,可以辞却不要,但是中国人为履行信用起见,宁可自己损失五千元,不情愿辞去那批货;所以外国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赞美中国人,说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得多。但是外国人在日本做生意的,和日本人订货,纵然立了合同,日本人也常不履行;譬如定货的时候,那批货订明一万元,在交货的时候,价格跌到五千元,就是原来订有合同,日本人也不要那批货,去履行合同,所以外国人常常和日本人打官司,在东亚住过很久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与日本人都做过了生意的,都赞美中国人,不赞美日本人。
至于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比方从前的高丽,名义上是中国的藩属,事实上是一个独立国家;就是在三十年以前,高丽还是独立,到了近来一二十年,高丽才失去自由。从前有一天我和一位日本朋友谈论世界问题,当时适欧战正剧,日本方参加协约国去打德国,那位日本朋友说:“他本不赞成日本去打德国,主张日本要守中立,或者参加德国来打协约国;但是因为日本和英国是同盟的,订过了国际条约的,日本因为要讲信义,履行国际条约,故不得不牺牲国家的权利,去参加协约国,和英国共同去打德国”。我就问那位日本人说:“日本和中国不是立过了马关条约吗?该条约中最要之条件不是要求高丽独立吗?为什么日本对于英国,能够牺牲国家权利去履行条约,对于中国,就不讲信义,不履行马关条约呢?对于高丽独立是日本所发起所要求,且以兵力胁迫而成的,今竟食言而肥,何信义之有呢?”?简直的说,日本对于英国,主张履行条约,对于中国,便不主张履行条约,因为英国是很强的,中国是很弱的。日本加入欧战,是怕强权不是讲信义罢!中国强了几千年而高丽犹在,日本强了不过二十年,便把高丽灭了,由此便可见日本的信义不如中国,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
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民族,袛有中国是讲和平,外国都是讲战争,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的国家。近年因为经过许多大战,残杀太大,才主张免去战争,开了好几次和平会议;像从前的海牙会议,欧战之后的华赛尔会议,金那瓦会议,华盛顿会议,最近的洛桑会议;但是这些会议中,各国人士公同去讲和平,是因为怕战争,出于勉强而然的,不是出于一般国民的天性。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之一,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
我们旧有的道德,应该恢复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我们自被满清征服了以后,四万万人睡觉,不但是道德睡觉了,连智识也睡了觉;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智识也应该唤醒他。中国有什么固有的智识呢?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智识中所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
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他放在智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我们祖宗对于这些道德上的功夫,从前虽然是做过了的;但是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后,这些智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一段话做口头禅,但是多是习而不察不求甚解莫名其妙的。正心诚意的学问是内治的功夫,是很难讲的,从前宋儒是最讲究这些功夫的,读他们的书,便可以知道他们做到了什么地步。但是说到修身、齐家、治国,那些外修的工夫,恐怕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专就外表来说,所谓修身、齐家、治国,中国人近几百年以来,都做不到;所以对于本国,便不能自治,外国人看见中国人不能治国,便要来共管。
我们为什么不能治中国呢?外国人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依我个人的眼光看,外国人从齐家一方面,或者把中国家庭看不清楚;但是从修身一方面来看,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些工夫,是很缺乏的。中国人一举一动,都欠检点,袛要和中国人来往过一次,便被他们看得很清楚。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国住过了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者是极大的哲学家像罗素那一样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国来,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于欧美,才赞美中国;普通外国人,总说中国人没有教化,是很野蛮的。推求这个原因,就是大家对于修身的工夫太缺乏;大者勿论,即一举一动,极寻常的工夫,都不讲究。譬如中国人初到美国的时候,美国人本来是平等看待,没有什么中美人的分别;后来美国大旅馆都不准中国人住,大的酒店都不许中国人去吃饭,这就是由于中国人没有自修的工夫。
我有一次在船上和一个美国船主谈话,他说:“有一位中国公使,前一次也坐这个船,在船上到处喷涕吐痰,就在这个贵重的地毡上吐痰,真是可厌”。我便问他:“你当时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我想到无法,袛好当他的面,用我自己的丝巾,把地毡上的痰擦干净便了。当我擦痰的时候,他还是不经意的样子”。像那位公使在那样贵重的地毡上都吐痰,普通中国人大都如此,由此一端,便可见中国人举动,是缺乏自修的功夫。
孔子从前说席不正不坐,由此便可见他平时修身虽一坐立之微,亦是很讲究的;到了宋儒时代,他们正心,诚意和修身的工夫,更为谨严;现在中国人便不讲究了。为什么外国的大酒店,都不许中国人去吃饭呢?有人说:“有一次一个外国大酒店,当会食的时候,男男女女非常热闹,非常文雅,济济一堂,各乐其乐;忽然有一个中国人放起屁来,于是同堂的外国人哗然哄散”。由此店主便把那位中国人逐出店外,从此以后外国大酒店就不许中国人去吃饭了。又有一次,上海有一位大商家,请外国人来宴会,他也忽然在席上放起屁来,弄到外国人的脸都变红了;他不但不检点,反站起来大拍衫裤,且对外国人说:“隘士巧士咪1[英文Excuseme的译音,意思是“对不起”。]。”这种举动,真是野蛮陋劣之极,而中国之文人学子,亦常有此鄙陋行为,实在难解。或谓有气必放,放而要响,是有益卫生,此更为恶劣之谬见,望国人切当戒之!以为修身的第一步工夫。
此外中国人每爱留长指甲,长到一寸多长,都不剪去,常以为要这样,便是很文雅。法国人也有留指甲的习惯,不过法国人留长指甲,只长到一两分,他们以为要这样,便可表示自己是不做粗工的人。中国人留长指甲,也许有这个意思,如果人人都不想做粗工,便和我们中国国民党尊重劳工的原理相违背了。再者中国人牙齿是常常很黄黑的,总不去洗刷干净,也是自修上的一大缺点。像吐痰、放屁、留长指甲、不洗牙齿,都是修身上寻常的工夫,中国人都不检点,所以我们虽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智识,外国人一遇见了便以为很野蛮,便不情愿过细来考察我们的智识。外国人一看到中国,便能够知道中国的文明,除非是大哲学家,像罗素那一样的人才能见到;否则便要在中国多住几十年,方可以知道中国几千年的旧文化。假如大家把修身的工夫做得很有条理,诚中形外,虽至一举一动之微,亦能注意,遇到外国人不以鄙陋行为而侵犯人家的自由,外国人一定是很尊重的。所以今天讲到修身,诸位新青年便应该学外国人的新文化,只要先能够修身,便可来讲齐家治国。现在各国的政治都进步了,袛有中国是退步,何以中国要退步呢?就是因为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推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修身;不知道中国从前讲修身,推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是很精微的智识,是一贯的道理,像这样很精微的智识和一贯的道理,都是中国所固有的,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智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
我们除了智识之外,还有固有的能力。现在中国人看见了外国的机器发达,科学昌明,中国人现在的能力,当然不及外国人,但是在几千年前,中国人的能力是怎么样呢?从前中国人的能力,还要比外国人大得多。外国现在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中国从前发明的。比如指南针在今日航业最发达的世界,几乎一时一刻都不能不用他。推究这种指南针的来源,还是中国人在几千年以前所发明的。如果从前的中国人没有能力,便不能发明指南针,中国人固老早有了指南针,外国人至今还是要用他,可见中国人固有的能力,还是高过外国人。其次在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东西,便是印刷术,现在外国改良的印刷机,每点钟可以印几万张报纸,推究他的来源,也是中国发明的。再其次在人类中日用的瓷器,更是中国发明的,是中国的特产,至今外国人竭力仿效,犹远不及中国瓷器的精美。近来世界战争用到无烟火药,推究无烟火药的来源,是由于有烟黑药改良而成的,那种有烟黑药也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这些重要的东西,外国今日知道利用发展他,所以他们能够有今日的强盛。
至若人类所享衣食住行的种种设备,也是我们从前发明的。譬如就饮料一项说,中国人发明茶叶,至今为世界之一大需要,文明各国皆争用之。以茶代酒,更可免了酒患,有益人类不少。讲到衣一层,外国人视为最贵重的是丝织品。现在世界上穿丝的人,一天多过一天,推究用蚕所吐的丝而为人做衣服,也是中国几千年前所发明的。讲到住一层,现在外国人建造的房屋,自然是很完全,但是造房屋的原理,和房屋中各重要部分,都是中国人发明的,譬如拱门就是以中国的发明为最早。至于走路,外国人现在所用的吊桥,便以为是极新的工程,很大的本领,但是外国人到中国内地来,走到川边西藏,看见中国人经过大山,横过大河,多有用吊桥的。他们从前没有看见中国的吊桥,以为这是外国先发明的,及看见了中国的吊桥,便把这种发明归功到中国。由此可见中国古时不是没有能力的,因为后来失去了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
但是恢复了我们固有的道德智识和能力以外,在今日的时代,还未能进中国于世界第一等的地位,像我们祖宗在从前是世界上独强一样。要想恢复到那样的地位,除了恢复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的长处,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还是要退后。我们要学外国,到底是难不难呢?中国人向来以为外国的机器是很艰难,是不容易学的;不知道外国所视为最难的,是飞上天。他们最新的发明的飞机,现在我们天天看见大沙头的飞机,天天飞上天,飞上天的技师是不是中国人呢?外国人飞上天都可以学得到,其馀的还有什么难事学不到呢?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用我们的本能,很可以学外国人的长处。外国人的长处是科学,用了两三百年的工夫,去研究发明,到了近五十年来,才算是十分进步;因为这种科学进步,所以人力巧夺天工,天然所有的物力,人工都可以做得到。
最新发明的物力是用电,从前物力的来源是用煤,由于煤便发动汽力,现在进步到用电,所以外国的科学已经由第一步进到第二步。现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计划,是要把全国机器厂所用的动力(即马达)都统一起来。因为他们全国的机器厂有几万家,各家工厂都有一个发动机,都要各自烧煤去发生动力,所以每天各厂所烧的煤和所费的人工都是很多;且因各厂用煤太多,弄到全国的铁路虽然有了几十万英里,还不敷替他们运煤之用,更没有工夫去运农产,于是各地的农产,便不能运出畅销。因为用煤有这两种的大不利,所以美国现在想做一个中央电厂,把几万家工厂用电力去统一;将来此项计划如果成功,那几万家工厂的发动机,都统一到一个总发动机,各工厂可以不必用煤和许多工人去烧火,只用一条铜线,便可以传导动力,各工厂便可以去做工。行这种方法的利益,好比现在讲堂内的几百人,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用锅炉去煮饭吃,是很麻烦的,是很浪费的;如果大家合拢起来,只用一个大锅炉去煮饭吃,就便当得多,就节省得多。现在美国正是想用电力去统一全国工厂的计划,如果中国要学外国的长处,起首便应该不必用“煤力”而用“电力”,用一个大原动力供给全国;这样学法好比是军事家迎头截击一样,如果能够迎头去学,十年之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
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著他。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我们到了今日的地位,如果还是睡觉,不去奋斗,不知道恢复国家的地位,从此以后,便要亡国灭种。现在我们知道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必可以学得比较外国还要好,所谓后来者居上。从前虽然是退后了几百年,但是现在只要几年便可以赶上。日本便是一个好榜样,日本从前的文化,是从中国学去的,比较中国低得多,但是日本近来专学欧美的文化,不过几十年便成为世界中列强之一。我看中国人的聪明才力,不亚于日本,我们此后去学欧美,比较日本还要容易。所以这十年中,便是我们的生死关头!如果我们醒了,像日本人一样,大家是提心吊胆,去恢复民族的地位,在十年之内,就可以把外国的政治经济和人口增加的种种压迫和种种祸害,都一齐消灭。
日本学欧美不过几十年,便成世界列强之一,但是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领土比日本大三十倍,富源更是比日本多,如果中国学到日本,就要变成十个强国。现在世界之中英美法日意大利等,不过五大强国,以后德俄恢复起来,也不过六七个强国,如果中国能够学到日本,只要用一国便变成十个强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便可以恢复到头一个地位!
但是中国到了头一个地位,是怎么样做法呢?中国古时常讲“济弱扶倾”,因为中国在政治文化正统思想上有了这个好政策;所以强了几千年,安南缅甸高丽暹罗那些小国,还能够保持独立。现在欧风东渐,安南便被法国灭了,缅甸被英国灭了,高丽被日本灭了。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么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没有大利,便有大害。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我们今日在没有发达之先,立定“济弱扶倾”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都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
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诸君都是四万万人的一份子,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这便是我们民族主义的真精神!
附录 【吴钩】《宋朝的小学生、中学生与大学生究竟上什么课程?》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初六日癸卯
耶稣2019年11月2日
宋代的学校分为大学、小学,没有中学之称。大学是太学等高等教育,相当于今天的大学阶段;小学是基础教育,又叫蒙学,启蒙教育的意思,相当于今天的小学;不过,宋朝各州郡设立的州学,实际上相当于今天的中学。
宋朝的蒙学是比较发达的,我们来看看宋朝人的描述:南宋杭州,“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这里的宗学、京学、县学是官学,即公立学校,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是私学,即民办学校、私立学校。
不独都城设有官学、私学,宋政府在各州县都建设了官学,包括小学。相比之下,私学的数目更多,比如在福建莆田,“十室九书堂”;在南剑州,“五步一塾,十步一庠”;在四川眉州,“凡一成之聚,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奠,士子私讲礼焉,名之曰乡校”。这里的“书堂”、“塾”、“庠”、“乡校”,都是民间兴办的私立小学,尽管宋人说得有些夸张,但宋朝私学之盛,可见一斑。甚至在偏远乡村,也有读书人,一位宋朝诗人写道:“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宋朝农村的孩子读书,一般是在十月份入学,叫做“冬学”。
宋朝的小学生平日要学习什么课程呢?朱熹编写过一份《童蒙须知》,说:“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也就是说,宋朝小学的教学内容,包括日常礼仪、生活习惯、基础文化知识与技能等,其中基础文化知识与技能的课程包括常用字读写、诗文阅读与创作(相当于语文课)、历史课、名物课(相当于自然课)、思想品德课,等等。
宋朝士大夫编写了大量蒙学教材,如朱熹编有六卷《小学》,吕祖谦编有《少仪外传》,黄继善编有《史学提纲》,方逢辰编有《名物蒙求》。影响最深广的宋朝蒙学教材,当属《三字经》与《百家姓》,它们与《千字文》合称“三百千”,是传统蒙学的经典教材。
《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人王应麟,清代学者评价说:“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言简意长,词明理晰,淹贯三才,出入经史,诚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也。”
《百家姓》的作者则是北宋初浙江的一名小民,姓名已佚失。因为是宋初浙江人所著,“赵钱孙李”四姓才会排在百家姓之首——赵是宋朝国姓,钱是当时钱塘国王之钱,孙是钱塘国王正妃之姓,李是后唐国主之姓。
除了《三字经》、《百家姓》,宋朝士大夫还辑录了《千家诗》,也是影响深远的蒙学教材。在宋朝之后的几百年里,传统中国最常用、最重要的蒙学教材,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可谓遗泽百世。
再来说说宋朝的州学与太学的课程。
宋代地方的州县学校也设置了科学课程,胡瑗主持湖州州学时,便将州学分为“经义”、“治事”两斋,其中“治事”斋开设治民、讲武、堰水和算历四项课程,要求学生“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宋代的书院也有科学课程,一生都致力于书院建设的朱熹主张:“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
宋朝政府并没有像明清统治者那样将科技发明视为“奇技淫巧”,加以禁绝;恰恰相反,朝廷常常对出色的科技发明者给予奖励,如冯继升改良了火药法,朝廷赐衣物束帛。在科技领域有突出才能的人通常会被列入“奇才异行”名录,可以直接选拔进政府机构。政府还有意识培养科技人才,在中央一级设立了多种专科学校,包括医学院、算学(数学)院、天文历法学校、武学院等,隶属于国子监。又实行奖学金制度,如医学院学生成绩为上等者,每月给钱十五贯,中等者给钱十贯,下等者给钱五贯。
我们要是以为古代的国子监、州县学、书院教授的仅仅是儒家经义,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想象。
宋代太学(相当于国立大学)的教学制度也堪称先进。经过王安石的改革,宋朝太学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三舍制”,学生被划分为外舍生、内舍生与上舍生三舍(相当于分为三个年级),每舍设若干斋(相当于班级),采用积分制,即学生的学习成绩量化为学分,成绩优秀的外舍生可升入内舍;内舍生成绩优异者,可升入上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将学生成绩量化计分、并按积分升等的教育制度。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宋代时,形成一座高峰,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应该说,宋朝对科技教育的重视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附录【吴钩】《宋朝的大学:不仅仅是太学》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赐稿
节选自 吴钩新书《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六月廿八日庚辰
耶稣2022年7月26日
宋朝的太学,为全国最高学府,我们不妨称之为宋代的“大学”。不过宋朝太学仅仅是国子监直辖的几所国立学校之一。太学之外,国子监还辖有多所学校:国子学、四门学、小学、辟雍。
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是北宋国子监下辖的几个专科学校。我记得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袁伟时教授曾说过:“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把数学、逻辑、法律等学科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熟读儒家经典成为主要上升渠道,导致知识阶层视野狭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但你只要略了解宋代的专科教育,便会知道袁教授所言过于偏颇,不合史实。
来看看宋朝的国子监设立了哪些专科学校——
1、律学,相当于法学院。北宋立国之初便置律学博士,传授法律。至熙宁六年(1073),于国子监下设律学,分“断案”、“律令”两个专业,断案专业主修刑名之学与案例试断;律令专业主修法理大义。律学所需的古今刑书,可向朝廷申请配备;朝廷颁布的法令,也需要关送律学。每月,律学会举行三次私试、一次公试。成绩优秀的律学生毕业后可赴吏部授官。兼修律学的太学生,在律学公试中获得第一等的成绩,可计入学分,相当于在太学私试中得第二等。
2、算学,相当于数学与天文学院,崇宁兴学期间设立,“生员以二百一十人为额,许命官及庶人为之”,入读的学生以天文、历法、算术、三式法(指卜筮之法)为必修课,再选修一门文化课,如《论语》、《孟子》,其“公私试、三舍法略如太学”,上舍的优秀毕业生可以授官。
3、书学,相当于文字学与书法学院,学生练习篆、隶、草三种字体,主修《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五书,兼通《论语》、《孟子》之义。公私试、三舍法同算学,只是毕业生所授官职“差降一等”。
4、画学,相当于美术学院,学生主要训练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题材的绘画,并学习《说文》、《尔雅》、《方言》、《释名》,士子出身的学生要求兼修两门文化课,杂流出身的人要求兼修一门文化课。考试主要为“试画”,“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并委托太学“试经义”。优秀毕业生授官待遇如书学。
5、武学,相当于军事与武术学校,学生主修武艺、兵法,考试时,先试军机策论,再试骑射之术。武学生毕业后可获授巡检、监押等职务。
6、医学,相当于医学院,初隶属于太常寺,崇宁兴学期间,考虑到“所有医工未有奖进之法,盖其流品不高,士人所耻,故无高识清流习尚其事。今欲别置医学,教养上医”,遂另建医学院,改隶国子监。
北宋医学分“方脉科”、“针科”、“疡科”三个专业。方脉科有点接近今人所说的内科,其学生主修大方脉、小方脉、风科等专业课,兼习王氏《脉经》、张仲景《伤寒论》;针科类似于今天的针炙科加五官科,其学生主修大针炙、口齿、咽喉、眼耳等专业课,兼习《针炙经》、《龙本论》;疡科接近今天的外科,其学生通习疮肿、伤折、金疮等专业课,兼习《针炙经》、《千金翼方》。
除了专业课,还有公共课,方脉科、针科、疡科三个专业的学生都需要学习《黄帝素问》、《难经》、《巢氏病源》、《补本草》、《千金方》。此外还有实习课:太医局在“近城置药园种药,其医学生员,亦当诣园辨识诸药”。
医学亦仿太学三舍法,“立上舍四十人,内舍六十人,外舍二百人”。外舍生升内舍生主要看私试与公试的成绩。内舍生升上舍生,以及上舍生能不能毕业,则不但看考试成绩,还要看“医治比校”,即行医实习的积分。
“医治比校”是这么设计的:给医学内舍生、上舍生每人发一本“印历”,定期派往太学、武学、律学、算学、艺学(即书学与画学)实习行医,医治患病的学生。诊治时候,必须在“印历”上“书其所诊疾状”,送回医学院盖章。然后按疾病的疗程,如实登记治疗结果:“愈或失”,并报医学院核实盖章。年中进行“比校”,合格的成绩分为三等:100%的治愈率为上等,给10个学分;90%的治愈率为中等,给9个学分;80%的治愈率为下,给8个学分。
在“医治比校”中获得10个学分的医学内舍生,可以申请试上舍,只要在考试中得到“平”的成绩,便能升舍;如果是上舍生获得10个学分,则可毕业授官,“听保明推恩”,一般是“选充尚药局医师”,或者安排为国子监及诸州府医学的教授;得到8个或9个学分的学生,则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才可以升补或毕业;只得到7个学分的学生,降舍,即从上舍降至内舍,或从内舍降至外舍;5个学分以下的学生,“屏出学”,即勒令退学。
说到这里,想起了一句宋诗:“太学诸斋拣秀才,出门何处是金台?”诗中的秀才,非指一般的读书人,也非指科举制度中的生员(明清时期,“秀才”方有这两个含义),而是指优秀的才俊之士;金台,为国家延揽士人的象征性建筑。太学设诸斋、分三舍,意在培养与遴选优秀的人才。太学之外,又置医学、律学、算学等专科学校,当然也是为了培养杰出的专业人才。宋朝才俊辈出,人文与科技成就都足称鼎盛,与其发达的教育制度是分不开的。
最后,顺便一说:唐宋时期的国子监是一个教育行政机构,下辖多所学校,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元明清时期的国子监只是一所国立学校,与从前的国子学相类。因此,虽然自唐至清均设有国子监祭酒一职,但唐宋时期的国子监祭酒是教育部长,元明清时期的国子监祭酒只是一所国立学校的校长而已。
附录【钱穆】《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
要谈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首先应该提到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精神和理想。此项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精神和理想,创始于三千年前的周公,完成于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此项教育的主要意义,并不专为传授知识,更不专为训练职业,亦不专为幼年、青年乃至中年以下人而设。此项教育的主要对象,乃为全社会,亦可说为全人类,不论幼年、青年、中年、老年,不论男女,不论任何职业,亦不论种族分别,都包括在此项教育精神与教育理想之内。
中国传统教育的宗教精神
在中国的文化体系里,没有创造出宗教,直到魏、晋、南北朝以后,始有印度佛教传入,隋、唐时代,乃有伊斯兰教、耶教等相继东来。中国社会并不排拒外来宗教,而佛教在中国社会上,尤拥有广大信徒。亦可说,佛教虽创始于印度,但其终极完成则在中国。但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佛教仍不占重要地位。最占重要地位者,仍为孔子之儒教。
孔子儒教,不成为一项宗教,而实赋有极深厚的宗教情感与宗教精神。如耶教、佛教等,其教义都不牵涉到实际政治,但孔子儒教,则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终极理想,故儒教鼓励人从政。又如耶教、佛教等,其信徒都超然在一般社会之上来从事其传教工作。但孔子儒家,其信徒都没入在一般社会中,在下则宏扬师道,在上则服务政治。只求淑世,不求出世。故儒教信徒,并不如一般宗教之另有团体,另成组织。
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教育即负起了其它民族所有宗教的责任。儒家教义,主要在教人如何为人。亦可说儒教乃是一种人道教,或说是一种人文教,只要是一个人,都该受此教。不论男女老幼,不能自外。不论任何知识、任何职业,都该奉此教义为中心,向此教义为归宿。在其教义中,如孝、弟、忠、恕,如仁、义、礼、智,都是为人条件,应为人人所服膺而遵守。
中国的这一套传统教育,既可代替宗教功能,但亦并不反对外来宗教之传入。因在中国人观念里,我既能服膺遵守一套人生正道,在我身后,若果有上帝诸神,主张正道,则我亦自有上天堂进极乐国的资格。别人信奉宗教,只要其在现实社会中不为非作歹,我以与人为善之心,自也不必加以争辩与反对。因此在中国文化体系中,虽不创兴宗教,却可涵容外来宗教,兼收并包,不起冲突。
中国儒家人品观:人人皆可为尧舜
在中国儒家教义中,有一种人品观,把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作评判标准,来把人分作几种品类。即如自然物乃至人造物,亦同样为他们品第高下。无生物中如石与玉,一则品价高,一则品价低。有生物中,如飞禽中之凰凤,走兽中之麒麟。水生动物中,如龙与龟,树木中如松、柏,如梅、兰、竹、菊。人造物中,如远古传下的钟、鼎、彝器,以及一应精美高贵的艺术品,在中国人心目中,皆有甚高评价。物如此,人亦然。故中国人常连称人物,亦称人品。物有品,人亦有品。天地生物,应该是一视同仁的。但人自该有人道作标准来赞助天道,故曰:“赞天地之化育”,中国人贵能天人合德,以人来合天。不主以人蔑天,亦不主以天蔑人。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有其天道观,亦有其人道观。有其自然观,亦有其人文观。两者贵能相得而益彰,不贵专走一偏。
中国人的人品观中,主要有君子与小人之别。君者,群也。人须在大群中做人,不专顾一已之私,并兼顾大群之公,此等人乃曰“君子”。若其人,心胸小,眼光狭,专为小己个人之私图谋,不计及大群公众利益,此等人则曰“小人”。在班固《汉书》的《古今人表》里,把从来历史人物分成九等。先分上、中、下三等,又在每等中各分上、中、下,于是有上上至下下共九等。历史上做皇帝,大富大贵,而列人下等中,乃至列入下下等的尽不少。上上等是圣人,上中等是仁人,上下等是智人。中国古人以仁智兼尽为圣人,故此三等,实是一等。最下下等是愚人。可见中国人观念,人品分别,乃由其智愚来。若使其知识开明,能知人道所贵,自能做成一上品人。因其知识闭塞,不知人道所贵,专为己私,乃成一下品人。故曰:“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此则须待有教育。苟能受教育,实践人道所贵,则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类的理想,乃使人人同为上等人,人人同为圣人,此是中国人的平等观。
中国人言人品,又常言品性品德。人之分品,乃从其人之德性分。天命之谓性,人性本由天赋,但要人能受教育,能知修养,能把此天赋之性,实践自得,确有之己,始谓之德。德只从天性来。天性相同,人人具有。人之与人,同类则皆相似,故人人皆能为尧舜。而且尧舜尚在上古时代,那时教育不发达,尧舜能成为第一等人,我们生在教育发达之后世,只要教育得其道,岂不使人人皆可为尧舜。若使全世界人类,同受此等教育熏陶,人人同得为第一等之圣人。到那时,便是中国人理想中所谓大同太平之境。到此则尘世即是天堂。人死后的天堂且不论,而现实的人世,也可以是天堂了。故说中国传统教育的理想与精神,是有他一番极深厚的宗教情趣与宗教信仰的。
中国人传统教育的理想与精神,既然注重在人之德性上,要从先天自然天赋之性,来达成其后天人道文化之德,因此中国人的思想,尤其是儒家,便特别注意到人性问题上来。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性由天赋,人若能知得自己的性,便可由此知得天。但人要知得自己的性,该能把自己的那一颗心,从其各方面获得一尽量完满的发挥,那才能知得自己的性。人心皆知饮食男女,饮食男女亦是人之性,但人的心不该全在饮食男女上,人的性亦不只仅是饮食男女。人若专在饮食男女上留意用心,此即孟子所谓养其小体为小人。
中国儒家人品观:文化多元
人的生命,有小体,有大体。推极而言,古今将来,全世界人类生命,乃是此生命之大全体。每一人之短暂生命,乃是此生命之最小体。但人类生命大全体,亦由每一人之生命小体会通积累而来。不应由大体抹杀了小体,亦不应由小体忽忘了大体。
儒家教义,乃从每一人与生俱来各自固有之良知良能,亦可说是其本能,此即自然先天之性。由此为本,根据人类生命大全体之终极理想,来尽量发展此自然先天性,使达于其最高可能,此即人文后天之性。使自然先天,化成人文后天。使人文后天,完成自然先天。乃始是尽性知天。若把自然先天单称性,则人文后天应称德。性须成德,德须承性。性属天,人人所同。德属人,可以人人有异。甚则有大人小人之别。有各色人品,有各类文化。
世界诸大宗教,都不免有尊天抑人之嫌。惟有中国儒家教义,主张由人合天。而在人群中,看重每一小己个人。由每一小己个人来尽性成德,由此人道来上合于天道。没有人道,则天道不完成。没有每一小己个人之道,则人道亦不完成。近代人喜言个人自由,实则中国儒家教义,主张尽性成德,乃是每一人之最高最大的自由。由此每一人之最高最大的自由,来达成全人类最高最大的平等,即是人人皆为上上第一等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儒家教义由此理想来教导人类,此为对人类最高最大之博爱,此即孔子之所谓仁。
中国儒家教育观:高人品高人格,方能为人师
中国儒家此一种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既不全注重在知识传授与职业训练上,更不注重在服从法令与追随风气上,其所重者,乃在担任教育工作之师道上,乃在堪任师道之人品人格上。故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若要一人来传授一部经书,其人易得。若要一人来指导人为人之道,其人难求。因其人必先自己懂得实践了为人之道,乃能来指导人。必先自己能尽性成德,乃能教人尽性成德,《中庸》上说:“尽己之性,乃能尽人之性。”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因其人品人格最高,乃能胜任为人师之道,教人亦能各自尽性成德,提高其各自之人品人格。
韩愈《师说》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其实此三事只是一事。人各有业,但不能离道以为业。如为人君,尽君道。为人臣,尽臣道。政治家有政治家之道。中国人常说信义通商,商业家亦有商业家之道。社会各业,必专而分,但人生大道,则必通而合。然人事复杂,利害分歧,每一专门分业,要来共通合成一人生大道,其间必遇许多问题,使人迷惑难解,则贵有人来解其惑。所以传道者必当授之业而解其惑。而授业解惑,亦即是传道。
中国儒家教育观:道义远重于职业
孔子门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子夏列文学科,孔子教之曰:“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则治文学科者,仍必上通于德行。子路长治军,冉有擅理财,公西华熟娴外交礼节,各就其才性所近,可以各专一业。但冉有为季孙氏家宰,为之理财,使季孙氏富于周公,此已违背了政治大道。孔子告其门人曰:“冉有非吾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但季孙氏也只能用冉有代他理财,若要用冉有来帮他弑君,冉有也不为。所以冉有还得算是孔门之徒,还得列于政事科。至于德行一科,尤是孔门之最高科。如颜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学了满身本领,若使违离于道,宁肯藏而不用。可见在孔门教义中,道义远重于职业。
宋代大教育家胡瑗,他教人分经义、治事两斋。经义讲求人生大道,治事则各就才性所近,各治一事,又兼治一事。如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从来中国学校,亦重专业教育,如天文、历法、刑律、医药等。近代教育上,有专家与通才之争。其实成才则就其性之所近,宜于专而分。中国传统教育,也不提倡通才,所提倡者,乃是通德通识。故曰:“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有了通德通识,乃为通儒通人。人必然是一人。各业皆由人担任。如政治、如商业,皆须由人担任。其人则必具通德,此指人人共通当有的,亦称达德。担任这一业,也须懂得这一业在人生大道共同立场上的地位和意义,此谓之通识。通德属于仁,通识属于智。其人具有通德通识,乃为上品人,称大器,能成大业,斯为大人。若其人不具通德通识,只是小器,营小事,为下品人。
中国儒家人品观:雅士即君子
中国人辨别人品,又有雅俗之分。俗有两种,一是空间之俗,一是时间之俗。限于地域,在某一区的风气习俗之内,转换到别一区,便不能相通,限于时代,在某一期的风气习俗之内,转换到另一期,又复不能相通。此谓小人俗人。大雅君子,不为时限,不为地限,到处相通。中国在西周初期,列国分疆,即提倡雅言雅乐,遂造成了中国民族更进一步之大统一。此后中国的文学艺术,无不力求雅化。应不为地域所限,并亦不为时代所限。文学艺术如此其它人文大道皆然。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此项大道,其实只在一个小己个人的身上,此一人便成为君子。但君子之道,并不要异于人,乃要通于人。抑且要通一大群一般人。故曰征诸庶民,要能在庶民身上求证。考诸三世,是求证于历史。建诸天地,是求证于大自然。质诸鬼神,是求证于精神界。此项大道,惟遇圣人,可获其首肯与心印。圣人不易遇,故将百世以俟。但此一君子,其实亦可谓只是一雅人。雅即通,要能旁通四海,上下通千古,乃为大雅之极。故既是君子,则必是一雅人。既是雅人,亦必是一君子。但没有俗的君子,亦没有雅的小人。只中国人称君子,都指其日常人生一切实务言。而中国人称雅人,则每指有关文学艺术的生活方面而言。故君子小人之分,尤重于雅俗之分。
中国传统教育,亦可谓只要教人为君子不为小人,教人为雅人不为俗人。说来平易近人,但其中寓有最高真理,非具最高信仰,则不易到达其最高境界。中国传统教育,极富宗教精神,而复与宗教不相同,其要端即在此
中国传统教育,因寓有上述精神,故中国人重视教育,往往不重在学校与其所开设之课程,而更重在师资人选。在中国历史上,自汉以下,历代皆有国立太学。每一地方行政单位,亦各设有学校。乡村亦到处有私塾小学。但一般最重视者,乃在私家讲学。战国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竞起,此姑不论。在两汉时代,在野有一名师,学徒不远千里,四面凑集,各立精庐,登门求教,前后可得数千人。亦有人遍历中国,到处访问各地名师。下至宋、元、明三代,书院讲学,更是如此。所以在中国传统教育上。更主要者,乃是一种私门教育、自由教育。其物件,则为一种社会教育与成人教育。孔子死后,不闻有人在曲阜兴建一学校继续讲学。朱子死后,不闻有人在武夷、五曲,在建阳、考亭兴建一学校继续讲学。更如王阳明,只在他随处的衙门内讲学,连书院也没有。中国传统教育之主要精神,尤重在人与人间之传道。既没有如各大宗教之有教会组织,又不凭借固定的学校场所。只一名师平地拔起,四方云集。不拘形式地进行其教育事业,此却是中国传统教育一特色。
唐代佛教中禅宗崛起,他们自建禅寺,与一般佛寺不同。可以没有佛殿,可以不开讲一部佛门经典。但有了一祖师,四方僧徒,云集而至。一所大丛林,可以有数千行脚僧,此来彼往,质疑问难。一旦自成祖师,却又另自开山,传授僧徒。禅宗乃是佛教中之最为中国化者,其传教精神,亦复是中国化。
中国儒家精神与理想:人生不能只是功利的
近代的世界,宗教势力,逐步衰退。西方现代教育,最先本亦由教会发动,此刻教会势力亦退出了学校。教育全成为传播知识与训练职业。只有中小学,还有一些教导人成为一国公民的教育意义外,全与教导人为人之道的这一大宗旨,脱了节。整个世界,只见分裂,不见调和。各大宗教,已是一大分裂。在同一宗教下,又有宗派分裂。民族与国家,各自分裂。人的本身,亦为职业观念所分裂。如宗教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法律家、财政经济家、企业资本家等,每一职业,在其知识与技能方面,有杰出表现杰出成就者,均目为一家。此外芸芸大众,则成无产阶级与雇用人员。好像不为由人生大道而有职业,乃是为职业而始有人生。全人生只成为功利的、唯物的。
庄子说:“道术将为天下裂。”今天世界的道术,则全为人人各自营生与牟利,于是职业分裂。德性一观念,似乎极少人注意。职业为上,德性为下,德性亦随职业而分裂。从事教育工作者,亦被视为一职业。为人师者,亦以知识技能分高下,非犯法,德性在所不论。科学被视为各项知识技能中之最高者。《中庸》说:“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大学》说“格物”,其最后目标乃为国治而天下平。朱子说:“格物穷理”,其所穷之理,乃是吾心之全体大用,与夫国治天下平之人生大道。近代科学,只穷物理,却忽略了人道,即人生之理。原子弹、核武器,并不能治国平天下。送人上月球,也非当前治国平天下所需,科学教育只重智,不重仁。在《汉书》的《古今人表》里,最高只当列第三等,上面还有上上、上中两等,近代人全不理会。中国传统教育之特殊理想与特殊精神,在现实世界之情势下,实有再为提倡之必要。
中国传统教育观:人皆有向上心,需要君子做榜样
而且中国传统教育理想,最重师道。但师道也有另一解法。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子贡亦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可见人人可以为人师,而且亦可为圣人师。中国人之重师道,其实同时即是重人道。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柳下惠并不从事教育工作,但百世之下闻其风而兴起,故说为百世师。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所以儒家教义论教育,脱略了形式化。只要是一君子,同时即是一师。社会上只要有一君子,他人即望风而起。又说:“君子之教,如时雨化之。”只要一阵雨,万物皆以生以化。人同样是一人,人之德性相同,人皆有向上心。只要一人向上,他人皆跟着向上。中国古人因对人性具此信仰,因此遂发展出像上述的那一套传统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精神。
不要怕违逆了时代,不要怕少数,不要怕无凭借,不要计及权势与力量。单凭小己个人,只要道在我身,可以默默地主宰着人类命运。否世可以转泰,剥运可以转复。其主要的枢纽,即在那一种无形的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上。此可以把中国全部历史为证。远从周公以来三千年,远从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年,其间历经不少衰世乱世,中国民族屡仆屡起,只是这一个传统直到于今,还将赖这一个传统复兴于后。这是人类全体生命命脉之所在。中国人称之曰:“道”。“教统”即在此“道统”上,“政统”亦应在此“道统”上。全世界各时代、各民族、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体系、各大教育组织,亦莫不合于此者盛而兴,离于此者衰而亡。而其主要动机,则掌握在每一小已个人身上。明末遗民顾亭林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内涵意义亦在此。
由于中国传统而发展成为东方各民族的文化体系,韩国人的历史,至少亦该远溯到三千年以上。即根据韩国史,我想亦可证成我上面之所述。我中、韩两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身负教育责任的,应该大家奋起,振作此传统精神,发扬此传统理想。从教育岗位上,来为两民族前途,为全世界人类前途,尽其最高可能之贡献。
认识传统就是认识自己
我要特别说明,我很喜欢这“传统”二字,因这传统二字,特别重要。但要认识传统,其事不易。好像有些时候,我们要认识别人反而易,要认识自己反而难。而且要认识我们东方人的传统,要比认识西方人的传统其事难。如中国有四千年、五千年以上的传统,韩国有三千年以上的传统,日本有二千年以上的传统。西方如法国、英国,只有一千年传统,美国只有两百到四百年传统,苏维埃没有一百年传统。
教育的第一任务,便是要这一国家这一民族里面的每一分子,都能来认识他们自己的传统。正像教一个人都要能认识他自己。连自己都不认识,其它便都不必说了。
对西方教育不能奉行“拿来主义”
今天,我们东方人的教育,第一大错误,是在一意模仿西方,抄袭西方。不知道每一国家每一民族的教育,必该有自己的一套。如韩国人的教育,必该教大家如何做一韩国人,来建立起韩国自己的新国家,发扬韩国自己的新文化,创造出韩国此下的新历史。这一个莫大的新任务,便该由韩国人自己的教育来负担。要负担起此一任务,首先要韩国人各自认识自己,尊重自己,一切以自己为中心,一切以自己为归宿。
但这不是说要我们故步自封,闭关自守。也不是要我们不懂得看重别人,不懂得学别人长处来补自己短处。但此种种应有一限度。切不可为要学别人而遗忘了自己,更不可为要学别人而先破灭了自己。今天,我们东方人便有这样的趋势,亟待我们自己来改进。
附录【钱穆】《改革中等教育议》
鄙人前撰《改革大学制度议》,粗陈涯略,间滋误会。或疑鄙意菲薄实科与专业,此在原文申说已明,无烦辩解。或疑鄙意提倡通学,有减低大学程度之嫌,则由时贤夙习,尊专业,蔑通学,故云尔。鄙文特主教育旨趣转换一方向,并与程度高下无涉。昔人论学,每言博约。博不即是通,必博而有统类而能归于约之谓通;专不即是约,约如程不识将兵,有部勒约束,又如满地散钱,以一贯串之。故约以博为本。而今之专业,则偏寻孤搜,或不待于博。就此言之,倡导通学,毋宁是提高程度也。或主中学教育应主通,大学教育应主专,此亦不了通学难企,误谓略具常识即为通,是又浅之乎视通矣。且学校教育与私人学问,判属两事。私人学问当各就性业,毕生从事;学校教育则为青年壮年人树立一共同基础,律可由此上进。今谓中学修其通,大学务其专,是欲以学校教育包办私人学问,代大匠斫,希不伤手。时论既多主提高中学程度以为大学专精之阶梯,爰草此文,再献刍荛。
各阶段之教育,本各有独特之任务,中学校非专为投考大学之预备而设。目前各中学程度,难免低落,此乃一时现象。若就民十七至民二十七此十年间江浙平津一带而论,则中学校课程,已不嫌其过松,而嫌其过紧。专就学业知识论,似乎所望于中学生者,已嫌其过高,而不嫌其过浅。中等教育本与大学有别。知识学业之传授,并不当占最高之地位。青年期之教育,大要言之,应以锻炼体魄,陶冶意志,培养情操,开发智能为主,而传授知识与技能次之。今日国内有一至可悲观之现象,厥为知识分子体魄与精力之不够标格。一二十岁上下之中学毕业生,已渐具书生气,精神意识已嫌早熟。至大学毕业,年未壮立,而少年英锐之气已销磨殆尽,非老成,即颓唐。社会政军商学各界领袖,大体年龄,较之欧美各国,比数相差几有二十至三十年之巨。中国各界主持活动之强固中心人物,率在四十前后,而欧美各邦,则六十七十不为老。大抵中国人一过三十,便无勇猛精进可言。一过五十,便无强立不返可言。精神意气早熟早衰,社会活力日以沦浙。倘更不于当前青年教育加意矫挽,国族前途,复何期望?
更论中国知识分子之毕生生活,大体自家庭入学校,自学校入社会,而此社会又大体以都市为限。莫非一温暖狭隘之境,不舍在花房中玻璃阳光下所煦育之一种盆景花卉也。其自少而壮,自壮而老,常缠绵于闺房之内,流连于城市之间。濈濈湿湿,蚁附纳集,既以丧其迈往之韵,复以研其敦庞之质。深山穷谷,惊浪骇涛,心魂既所不接,神情为之噩胎。筋骨柔脆,意兴卑近。当其在学校,非不言卫生,而卫生特享受之别名。非不言运动,而运动仅游戏之余事。其体魄之完固,精力之弥满,姑勿与并世欧美相较,回视百年前吾济所最鄙视之八股时代,盖犹有逊色焉。彼时一秀才,赴乡会试,三年一度,以交通之不便,近者数百里,远者数千里,经月累时,犹得以跋涉山川,冒历风霜,识天地之高厚,亲民物之繁变。其所以强身体而壮精神之道,有非今日学校青年所能梦想。今则掩目于书本文字之中,放胆于朋偶罄咳之侧,体魄衰而精力糜,意志不坚强,情操不高洁,智能不开敏,而矻矻焉唯知从事于知识技能之传习,造诣有限,运用无力,根本已拨,妄希花果,亦多见其不知务矣。
窃谓今日中学教育,当痛惩旧病,一变往昔偏重书本之积染,而首先加意及于青年之体魄与精力。当尽量减少讲堂自修室图书馆工作时间,而积极领导青年为户外之活动。自操场进至于田野,自田野益进至于山林,常使与自然界清新空气接触。自然启示之伟大,其为效较之书本言说,什百倍徒,未可衡量。昔德人于前次大战失败后,即主以山林自然生活恢复其青年之内心活力。吾国近百年来,全国上下,麻醉于婴粟,沉酣于麻雀,精神意趣,束缚于门庭廖邑之间。毒雾弥漫,未有所廓清。非大加荡涤,振奋无由。当使学校一切田野化、山林化,使青年一入学校,恍然于一种新生命新境界之降临。庶足以扫除国人宴安于闺门迷恋于都市之沉冗,而后身体精神知识事业始有可商。
夫教育精神,贵能因时设施,非有成局定格可以永遵勿渝也。今国民党人常言忠实同志,此言最堪味。今国人所缺,正在忠实,而所鹜则为聪明。聪明日增,忠实日减。聪明即闺房城市之习,忠实则田野山林之气。抑聪明者尚知,忠实者尚行。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深感时弊,而倡知难行易之教。其用意在励国人之起而行,非奖国人之坐而知。乃今国人群相曲解,谓唯其知难,故当勉于求知。不知尊所闻则高明矣,行所知则广大矣。一国事业,知者居其一,行者居其百。今日国人大病,不在知之不足,而在行之无实。国家社会各方面所要之人才,非患其不聪明,而患其不忠实。非患其无知,而患其不行。今日之病,非白痴,非狂惑,乃瘫痪之与萎缩也。而今日国家教育,姑以最好评语加之,则一种彻头彻尾之尚知教育也。此正如以水救水,以火救火,其何能济?
抑又有进者。知贵乎个别之钻研,行贵乎共同之协调。故务知者其群涣,励行者其体凝。务知,故各以空言争领导;励行,故互以实践期成绩。吾国自民四五提倡新文化运动以来,承学之士,莫不曰自由,曰解放。以个性伸展为旗帜,目礼教为吃人之工具。以大群为小我之桎梏,以冲决网罗打破枷锁为斗士之光辉。而流弊所届,特立孤诣之士未见其多,泛驾逸轨之象则层出无已。今日对症发药,固当裁抑小我,奖进群育。纳之轨物,宏以大道矣。
然尚知尚行,特教育精神畸轻畸重之间,非谓其截然划然如鸿沟之不可逾越也。以旧教育拟之,尚知乃诗书之教,尚行则礼乐之教也。儒者谓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以今日学校课程言,体操唱歌即犹礼乐。衡以儒家理论,此两科当为学校教育之最高科目。日日必修,不可或缺。师生并习,无分上下。大抵初级中学应以乐为主而礼副之,高级中学则以礼为主而乐副之。初级唱歌,宜多制发扬蹈厉之辞,继以宏大和平之旨。以大群合唱为主,以舞蹈进行为助。务求活泼动荡,开拓其情趣,畅悦其胸襟。而又辅之以晨夕之劳作,健身之游戏,以及郊外之远足。至高中则以严格之军事训练与大规模之山林眺览夹辅并进,而以竞技运动与庄严肃穆之歌曲辅之。其他如童子军青年营等训练,皆当切实重视,不得目为课业余暇之消遣与点缀。凡学校师生生活,皆当以礼乐为中心,以锻炼体魄,陶冶意志,培养情操,开发智慧为目的。而知识技能之传习,则降而次之。孔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子路谓“何必读书,然后为学”,皆此意也。
或疑若是则学业将有益降愈下之弊。不知苟其人体魄完固,精神充健,意志定而情趣卓,则智慧自开敏,知识技能虽粗引其绪,他日置身社会,自能得路寻向上去。孔子所谓吾见其进,未见其止也。苟既体弱而神茶,志摇而情卑,智慧昏惑,不得安宁,而徒皇皇汲汲于知识之灌输,技能之修习,今日学校青年之仿徨歧途,烦闷苦恼,激而横溃,疲而半废,前车之覆,正复可鉴。抑学校课程,果能改弦易辙,则别自有取精用宏事半功倍之道。程度之提高,不在于繁其课目,多其钟点,而在乎门类与内容之精选及教法之严格。窃谓今日学校课程,以别择不精,滥杂铺张,而浪费精力者,居三之一。以教法不严,鲁莽灭裂,而涂塞聪明者,又居三之一。若能删其芜秽,抉其蓄华,专力并赴,则课程虽简,而学业自进。合之上文所论,正可收相得益彰之效。
尝试追求今日学校课程病根,盖亦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则高唱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而结果则支离破碎,漫无准绳。一则提倡科学教育而未得其方,大学专门化之风气,浸寻波及于中学。一切课目,皆趋于形式僵化,未能提其精英,活泼运用。前者之弊,其著在文科。后者之弊,其著在理科。一则古今中外,浅深雅俗,樊然杂陈,如百袖之衣,天吴紫凤,破布败絮,裙披拚凑,陆离光怪,而不问其何以被于体。一则声光热力动植生矿,上自天文,下至地质,山珍海错,食前方丈,而不问其何以纳诸胃。前者病在驳而不纯,后者病在积而不化。一则沙石俱下,无益营卫。一则酿肥太过,徒增郁闷。今日中学课程之改进,唯有二道:曰精,曰简。庶使学者精力充沛,神智自生。否则买菜求多,学海深广,青年力弱,终有没溺之患。
又近制中学分高初两级,课程多一周环。初中学龄仅当十二三岁,即须离家外宿。学校既护育难周,稚年身心,受损匪细。谓宜仍旧贯,后期小学增一年,而高初中并合为五年制。又宜多设各项补习学校、职业学校、专修学校等,与普通中学并行,一如大学之例。
上之所陈,颇多乖背时风。如课程之改订,师资之培养,皆非仓促可希。苟非其人,虽有良法,亦莫所施。徒更规章,转滋扰动。唯事关国家民族复兴百年大计,心之所蓄,终不敢默。非敢故标高论,轻求更张。尚望公私贤达,详赐考虑。倘得于大中两级,妙选人才,各办试验学校一二所,侯成效确著,再谋推布,或亦稳健之一法也。
(三O,四,二O,《大公报》星期论文。)
附录【钱穆】《改革大学制度议》
今日大学教育有一至要之任务,厥为政术与学术之联系。抗战期间,后方政治之重要,不亚于前线之军事,其理尽人所知。而抗战结束以后,百孔千疮,万端待理,政治事业之重要与其艰巨,更将十百倍于今日。而政治事业之推动与支持,则首赖于人才。人才之培养,系唯大学教育之责。抑政治事业,就广义言之,不仅于居官从政。社会各方面各部门种种事业之推动支持,均有赖于适当之人才。亦必俟社会各方面各部门事业均有适当人才为之推动支持,而后其政治乃有基础可以发皇。在朝在野,相得益彰。此项社会各色中坚领袖人才之培养,亦唯大学教育之责。而不幸吾国最近二十年间大学教育之精神,似未注意于此。
吾国最近二十年间大学教育所注意之点,举要言之,约有三端。一曰校舍之建设,二曰图书仪器以及卫生体育种种物质上之设备,三曰院系之展扩,教师之罗致,以及课程之增新。
首言建筑。举其著者,北自北平清华,南至广州中大,东自首都中央大学,中越武汉,西至成都川大,其轮焉奂焉,门墙之美富,宫室之壮丽,彰彰在人耳目,此不得不认为是吾国最近大学教育精神贯注之一端。然与艰难兴邦,艰苦卓绝,实事求是之旨,则不能相符。居移气,养移体,而今日国家社会所需之人才,则在彼不在此。
次言设备。其一部分图书仪器之购置,与第三项相关,又一部分则属于生活起居上之讲究,与第一项相关。若大学校舍之建筑,稍能因陋就简,不事铺张,则内部设备,亦自大可省削也。
第三项当为大学教育最高目的所在。然仅仅注重于智识之传授,无当于人格之锻炼,品性之陶冶,识者讥之,谓此乃一种智识之稗贩。大学譬如百货商店,讲堂则其叫卖炫鬻之所也。抑就鄙见论之,即谓大学教育最高任务唯在智识之传授,而今日国内大学之院系析置,课程编配,亦大有可资商榷者。夫学术本无界划,智识贵能会通。今使二十左右之青年,初入大学,茫无准则,先从事各人之选科。若者习文学,若者习历史,若者习哲学,若者习政治、经济、教育。各筑垣墙,自为疆境。学者不察,以谓治文学者可以不修历史,治历史者可以不知哲学,治哲学者可以不问政治。如此以往,在彼目以为专门之绝业,而在世则实增一不通之愚人。而国家社会各色各门中坚领袖人物,则仍当于曾受大学教育之学者中求之。生心害事,以各不相通之人物,而相互从事于国家社会共通之事业,几乎而不见其日趋于矛盾冲突,分崩离析,而永无相与以有成之日。
再进而一究各院系课程之编配,则其细已甚。更有甚者,国难以前,国内最负时誉之大学,莫不竞务于院系之析置,教授之罗聘,以及课程之繁列。一学系教授往往至七八人,课目往往至一二十门。而此等课目,则皆此等教授之专门绝业也。二十左右之青年,初入大学,茫无准则,于选科之外,又继之以选课。治文学者,或治甲骨钟鼎,或治音韵小学,或治传奇戏剧,或治文艺创作,亦复各筑垣墙,自为疆境。其于文学之大体,则茫然也。其他治历史哲学以往者,亦复尔尔。近人有讥中国教育为一种循环教育者,其意谓受教育者无当于国家社会之用,仅能循环不息,仍以其受教者教人。此亦浅言之耳。今日一大学国文系毕业之学生,即深感不能担负中学国文教员之重任。何者,彼之所治,乃专门绝业,如甲骨、钟鼎、音韵、小学、传奇、戏曲、文艺创作之类,皆非中学国文课所需。中学国文课所需者,乃一略通本国文字文学大义之人才,而今日大学教育,即绝不注意乃此。今日大学课程之趋势,愈分愈细,如俗所云钻进牛角尖,虽欲循环,而不可得也。
概括言之,今日国家社会所需者,通人尤重于专家。而今日大学教育之智识传授,则只望人为专家,而不望人为通人。夫通方之与专门,为智识之两途,本难轩轾。吾国今日大学制度之渊源,袭自欧美。读吾文者,必将以欧美大学制度为护符而生抗议。然欧美政治社会与中国未能尽同。必俟社会政治各色各部皆有中坚领导人才推动支持,撑得一局面,粗粗安定,粗粗像样,而后专家绝业乃得凭借而发抒。欧美社会政治各方面比较已有一粗粗安定像样之局面,而中国则否。故中国大学教育所当着意植培之人才,自当与欧美稍异其趣。且就学术而论学术,一门学术之发皇滋长,固贵有专家,而尤贵有大师。大师者,仍是通方之学,超乎各部专门之上而会通其全部之大义者是也。一部门学术之有大师,如网之在纲,裘之有领,一提挈而全体举。今欧美著名大学之讲座,此等大师,往往有之。而中国挽近学术,一切稗贩自欧美,传其专业较易,了其通识则难。故今日国内负时誉之大学,其拥皋比而登上座者,乃不幸通识少而专业多。如此则将使学者不见天地之大,古今之全体,而道术将为天下裂。昔者庄生之所怖,行且再见于今日。况欧美分系分科之制度,亦已渐为彼中有识者所不满,而国内最近大学课程之变本加厉,则尚有非欧美之所能企及者乎?物极必反,穷则思变。其细已甚,不可为继。此今日大学课程之谓矣。
论者率谓大学教育,不当偏重智识之传授,即同时应注意及于学者人格之锻炼,品性之陶冶,于是而有导师制度之倡议。然就鄙见所及,则今日教育部所欲积极推行之导师制,乃与现行大学教育根本精神扞格不相融。若仅求于现行大学制度中硬插进一导师制度,正如于现行全部大学课程中硬插进一门党义与一门军事训练耳。上下相蒙,视为具文,固无不可。真欲求其收相当之效果,则非徒绝不可得,抑且必得其正相反者。
私意以为现行大学制度,实有根本改革之必要。而改革大纲不外两端。一曰缩小规模,二曰扩大课程。请先言缩小规模。窃谓将来之新大学,应以单独学院为原则。其主干曰文哲学院,理工学院,其他如农学院,矿学院,森林、畜牧、纺织、渔业等诸学院,不妨各就需要,择地设立(其年限不妨较文哲理工学院稍短)。唯法律学院与医学院,应以毕业文哲理工学院或肄业二年以上者入之,与他学院不平行。每一学院之学生数,以二百人至四百人为限,最多不得超过五百人。次言扩大课程。窃谓每一学院之课程,应以共同必修为原则,而以选课分修副之,更不必再为学系之分别。以文哲学院言,其课目应包括现有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教育等各系之主要课目,而设立略通大义之学程。如中外名著研读,中国文学史,中西通史,及文化大纲,中外人文地理,中西圣哲思想纲要,政治学经济学大纲,教育哲学及教育方法等。并应兼习科学常识,如天文、地质、生物、心理学等各门之与文哲学科相关较切者。此项共通必修之学程,应占大学全学程二分之一以上。学者于研习此项共通必修学程之外,同时亦得各就性近,分习选科。此项选科之开设,一方就各学院所聘教授学业之专长,一方亦兼顾各学科之重要部分,为学者开示途辙。各学科之课程不必求备,各学者之选习,亦不必求专。要之大学教育之所造就,当先求其为通人而后始乃及于专家。而细碎无当大体之学程,则尤以少设为是。关于理工方面,笔者一无所知,不敢妄有所述。唯尝询之于理工方面之通人及有志青年,亦多病今日学校开设学科之细碎,与夫基本智识之不够。则其受病,盖亦与文哲方面略似。窃谓亦当如文哲学院办法,理工合院,不更分系,多授基本通识,而于本国通史及中西圣哲思想纲要二科,亦必兼治,以药偏枯之病。然必有为今日造就专家教育辩护者,其论点计必举实用主义为依旧。唯即就实用言,通人达才之在今日,其为用尤其于专家绝业。十数年来,学者争以文科为无用,而竭力提倡理科。彼不知一国社会教育政治经济各方面苟无办法,则其自然科学亦绝难栽根立脚,有蒸蒸日上之望。今自抗战以来,学风之变,激而愈远。投考理学院之学生,群然转向而考工学院。试问理学院无基础,工学院前途何在。若就文法学院论,则哲学系早有关门之势,最近文学系亦渐渐有追随哲学系而闭歇之倾向。稍次为历史系,较盛者为政治系,尤盛者为经济系。试问一国之政治不上轨道,经济岂能独荣。亦未有其国人全昧于已往之历史,而政治可以有办法者。亦未有其人绝不通文学哲学,而可以通史学者。仅以实用主义谈教育,必使学者专务于谋出路,寻职业,自私自利,只图温饱。而整个教育精神,亦必陷于急功近利,舍本而逐末。尝发狂论,谓学者竞舍理学院入工学院,更不如离弃大学而入汽车行之为愈。教育精神自有其大者远者,此则唯通才达识者知之,擅一才一艺以绝业名专门者,往往不知也。
若就鄙见所及,创立不分系之学院制,其学成而去者,虽不能以专门名家,然其胸襟必较宽阔,其识趣必较渊博。其治学之精神,必较活泼而真挚。文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之智识,交灌互输,以专门名家之眼光视之,虽若滥杂而不精,博学而无可成名,然正可由是而使学者进窥学问之本原,人事之繁赜,真理之奥衍,足以激动其真情,启发其明智。较之仅向一角一边,汲汲然谋学成业就,有以自表见者,试问由其精神影响其事业,其为用于国家社会者孰大。必学术丕变,而后人才蔚起。上述国家社会各色各门之中坚领袖人才,可以推动支持一种事业,撑成一种局面者,殆将于此求之也。其有刻意潜精,愿毕生靖献于一种专门学术之研究者,则于普通学院之上复设研究院,以资深造。
若论人格之锻炼,品性之陶冶,此亦学业进行中应有之一项目。苟治学为人,可以绝然分为两事,则其学之与其人,亦居可见。依鄙论,大学有教授,即不必再有导师。若大学教育能有造就通才之师资,则其人格之锻炼与夫品性之陶冶,亦已一以贯之矣。更不必骑驴而觅驴,叠床而架屋也。诚使将来之大学,变为不分系别之独立学院,其校长与教务长对于全校四五百学生之生活与性情,必能熟悉无遗,因材施教,始有可能。而全校教授,最多亦不至超出二三十人之数,可由校长教务长斟酌尽善而加聘请。其学术行谊,精神意气之相投,较之今日一大学文法理工学院教授百许人相集合,牟牟然各不相认识,各不相闻问者,亦必判然有间。学者耳濡目染,较有轨辙可寻。教授之于学生,纵不能一一全识,亦必认得其十分之六七。(以不分系故)而学生之于教师,则大抵皆可全识,不致路途相遇,掉臂而过之。(以不分院故)所谓如家人父子然,以人格相感化者,不必在上者之提倡,而自有其境界。不然,如今日者,全校三四院,每院六七系。教授一二百,学生数千人。为校长者,能以权诈术数维持学校不闹风潮不罢课,已为幸事。学生如入五都之市,目迷五色,耳乱七音。教授之来也,如一沤之漂浪于大海,虽有深愿,莫知所施。非专门绝业,不足以撑门面;非标新立异,不足以耸观听。学风之弊坏既极,更何论于人格之锻炼,与品性之陶冶。
近人亦有目睹大学教育之弊病,而不能洞察其症结所在,遂提倡恢复宋明书院旧统者。然书院亦已陈之刍狗,非如海上灵方,百病皆效也。窃谓昔日书院旧制,虽有其特点,而近代大学制度,至少有胜于书院制者两端。一为讲堂授课制。原原本本,首尾条贯,表里精粗,无所不到。昔人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窃谓今之讲堂制,苟遇良师,则一年授课,实胜如十年之勤读也。二曰课目分授制。各就专长,分门别类,兼收广畜,不名一师,实足以恢张智能,开拓心胸。较之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言者,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计。书院制所特胜于现行大学者,在其规模之狭小,师生有亲切之味,群居无叫嚣之习。若如鄙论,将来新大学以单设独立学院为原则,则庶兼二者之长,而无二者之缺尔。
今国难方殷,大学教育之缺陷,方更彰著。昔日各大学之建筑设备,大多化为瓦砾,荡为灰烬。学校于播迁流离之余,亦莫不因陋就简。学课之其细已甚者,渐不足以餍学者之望。较者亦苦于穷搜擗摘之无所施其技,而几于倚席不讲。因势利导,庶其在是。窃谓来日之大学,贵乎艰苦卓绝,而不贵乎铺张扬厉。贵乎实事求是,而不贵乎粉饰门面。贵乎淡泊宁定,而不贵乎热闹活动。规模不厌其小,而课程务求其大。所以作人才而培邦本者,其影响于建国前途实非细鲜。粗发鄙愚,窃愿邦人君子一商讨之。
附录【钱穆】《从整个国家教育之革新来谈中等教育》
中国创办新教育,自前清同治初元迄今八十年,始终不脱两大病。一曰实利主义,一曰模仿主义。实利主义之病,在乎眼光短浅,不从本源处下手。模仿主义之病,则在依样葫芦,不能对症发药。其实二病仍一病也。病在始终缺一全盘计划与根本精神。我所谓全盘计划与根本精神之教育,当名之曰国家教育。而前清以来八十年之教育,则殊与国家教育无涉。当其最先所设学校,只限于广方言馆水陆师学堂乃至格致书院之类,充其量,不过欲造就少许翻译人才军事人才与制造机械之人才而止。学外国语言文字,根本只为外交作翻译之用。学格致,根本只为军事上种种机械制造之用。自始便无一段精神认识到国家教育之深处。此由一种短浅的实利主义作祟,而模仿主义亦自依随而起。此一病直到民国初年,科举既废,政体既改,国人渐渐觉悟教育不仅为翻译与制造。一时目光,渐渐从军事与外交转移到政治法律经济诸部门,又更进而推及于文哲历史艺术各类。当时乃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而溯源寻根,仍还自前清同光以来之思想一气呵成。所异者,前一期乃实利主义为主而模仿主义副之,此一期则模仿主义为主而实利主义副之。而紧接新文化运动之后者,乃为科学救国与科学教育之呼声。其所谓科学教育者,依然缺乏一根本精神,无当于国家教育之深旨。就其实,仍以实利主义与模仿主义为支撑。不过又复以实利主义为主而模仿主义为副,实利与模仿二者之间,稍有畸轻畸重之转变而已。此乃民十八以来之大体情形。风尚所趋,近几年来各大学新生投考,报工学院者异常拥挤,而理学院则寥寥。文法学院独一经济学系最盛,而经济系的课程,亦只偏向于银行簿计会计管理之类,绝少对经济学原理有兴趣者。哲学系最不受人注意。而五人中至少四人学西洋哲学,至多一人学中国哲学。文学方面则十人中至少八人学西洋文学,至多两人学中国文学。此乃当面之事实,事实后面透露出一种心理。此种心理之倾向,便足表示一时代之风尚。而此辈中学青年投考大学时之心理倾向及其风尚之来源,则不得不说是教育精神所感召。此种教育精神,直从前清同光以来,一路从源头上看,又从当前实际情形看,不能不说其仍只为实利主义与模仿主义之作祟。若非为实利主义,何以群趋工科而不习理科?若非为模仿主义,何以群习西洋文学哲学而鄙弃本国文哲?所以民国三十年来之新教育,似乎依然摆脱不掉模仿与实利。实利是其目的,模仿是其手段。实利非不该讲,模仿非不该有。然若仅以模仿希冀实利之心理与见解为国家教育之重心,则实利既不可得,而模仿亦且不可能。我们的教育精神与教育理论,实有再反省与再讨论之必要。
今当针对时弊,提出两口号。一曰文化教育,一曰人才教育。此两口号亦互为表里,乃主以国家民族传统文化来陶冶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文化教育可以纠正新文化运动以来之一味模仿。人才教育可以包括时下科学教育专重实利主义之偏狭。所谓人才教育者,不仅限于自然科学之一面,而政法经济文哲历史艺术诸门亦已兼容并包。此种人才,求其能真切爱护国家民族,求其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则必以国家民族自本自根之传统文化为陶冶。否则若其人对英国文学哲学英国历史艺术乃至英国一切政法经济之本末源委知之甚悉,而对吾本国之此诸项目一无所知,则其人中心爱护英国之真诚必较其爱护本国者为更深更切。而其人之服务于本国社会,势必多所扞格,多所膈膜,不能为本国国家民族所理想要求之人才。此理至为显明。科学可以无国界,政法经济文哲史艺诸科不能无国界。科学人才虽可由留学教育而造就,政法经济文哲史艺诸科之人才,则必自本自根由自己传统文化为陶冶,非外国教育所能代劳。若国内政法经济乃至文哲史艺诸门皆无人才,皆无出路,则纵有外国教育所代劳而造就之科学人才,亦将感英雄无用武之地之苦痛。故科学教育仅当为人才教育之一部门,当于国家教育之全盘计划下有其地位与效用。而国家教育之全盘计划,则必于国家民族自本自根之传统文化有较深之认识与重视。故讲求国家教育之全盘计划与根本精神,实舍文化教育与人才教育莫能当。
中等教育为国家教育之一环,故中等教育亦当以文化教育与人才教育为主体。若根据此项意见,则当前之中等教育实有多需改正之处。目前中等教育第一大病,在仅以中等教育为升入大学教育之中段预备教育。而大学教育之终极目标,则为出洋留学。换言之,出洋留学,乃不翅为吾国家教育之最高阶层。故国内各大学各科教科书,几乎十之七八以采用西洋原本为原则。大学新生,以先通一种外国文为及格标准。而进入大学以后,则以径读西洋原本教科书及进而选修第二外国语为普通之常例。通常所谓第一外国语者,大体乃为英文。故中学教育之中心责任,乃不啻为投考大学之英文补习学校。学生在各科学程上所化之精力,几乎强半为修习英语之时间。然若此学生将来并无升入大学之机会,则其研习英语之工夫亦强半等于白费。欲矫此弊,首宜厘革大学课程。尤要者,莫如一切教科书均以用本国文字为原则。中国兴学八十年,自有国立大学亦逾四十年。前清光绪二十四年举办国立京师大学筹备章程有于上海设编译局,各学科除外国文外,均读编译课本一条。乃至今逾四十年,国立大学各学科仍无编译完备之课本,仍要借用外国原本教读。抑且一般见解,不以此为可羞,转以此为可夸。此实四十年来国家教育之失败,亦四十年来留学教育疲缓不济事之奇耻大辱也。不仅大学各学科教本必需用本国文字编译者为原则,即各学科基本参考用书,亦当由国立编译机关作大量有计划之翻译。庶使学者省其攻读外国语文之精力,以从事于学科本身之精研与深究。尤要者,国家必设法提高本国大学之地位,勿再以出洋留学为国家教育之最高阶层。苟使此两事办有成绩,则庶乎可以走上文化教育人才教育之趋向。否则全国青年,当其有志向学,即日夕孜孜于外国语言文字之攻读。及其成学有立之最高阶段,又全付其责任于外国人之手。如是而言文化教育人才教育,真所谓南辕北辙,将愈趋而愈远。更不如缘木求鱼之仅止于不可得而已也。
国家教育若诚有意于文化教育与人才教育之两目标,则又有一事必当注意者,即国立大学当以文理学院为首脑,为中心。其他特殊专门学科如医工农矿渔牧诸类,不妨因地制宜,多设独立学院,与大学中心理工学院分道扬镳。盖前者为文化人才教育而设,后者则为养成职业技术之专门人才而设。两者旨趣不同,分之则两美,混之则两损也。若大学有此分设之规定,则中学问题亦迎刃而解。中学亦应分普通中学与职业中学两类。普通中学为文化人才之教育而设,职业中学则为养成职业技术之专门人才而设,性质亦复不同。凡受普通中学之教育者,主旨与大学中心文理学院之教育同,皆以国家民族传统文化陶冶真切爱护国家民族与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为主。是为国家教育之骨干。而各项中学职业学校与各项专门独立学院则如枝叶之附丽。其设科施教,不妨偏于实用,不妨模仿外国之成规,然皆非所语于国家教育之主干。
若如上论,普通中等教育之主要任务,实当以文化教育为手段,以人才教育为目标。换辞言之,即注重于国家民族传统文化之陶冶。经此一番陶冶而出者,则当期其为国家民族所理想要求之人才也。本此旨趣,中学教育之中心课务,实当以本国语言文字之传习为主。夫科学知识可以分门别类,而人生所需要之知识,实不尽于科学知识。因此有许多知识虽为吾人所必需,而往往无门类之可分。因此学校教育若以科学教育为中心,必将遗漏好许为人生所必要之知识。若以文化教育为中心,则此病可免。而文化教育之最重要者,则首推文字教育。一国之文字,即此国家民族传统文化之记录之宝库也。若使青年能读一部《论语》,读一部《庄子》,读一部《史记》,读一部《陶渊明诗》,彼之所得,有助于其情感之陶冶,意志之锻炼,趣味之提高,胸襟之开广,以至传统文化之认识,与自己人格之养成,种种效益,与上一堂化学听一课矿物所得者殊不同。然不得谓其于教育意义上无裨补。抑且毋宁谓教育之甚深意义,实在此而不在彼。今日中国学校中对于本国文字之教育,我无以名之,名之曰迁就之教育。夫教育宗旨本在悬一高深之标格,使低浅者有所向往而赴。迁就教育则不然。教育者自身无标格,乃迁就被教者之兴趣与程度以为施教之标格。夫学问有阶级,不可躐等,此义尽人皆知。然文字教育则有时贵乎投入亲验,使之当面觌体,沉潜玩索之久,而恍然有悟,豁然有解。此所谓欣赏,而阶级之制限有时为不适用。今国人每议本国文字为深玄难解,不知此当投入亲验。惟读《庄子》可解《庄子》,惟读《史记》可解《史记》,若先斥《庄子》《史记》为难读,先读其浅者易者,而文字文学之阶层亦重重无尽,若取迁就主义,则更有其尤浅尤易者。日亲浅易之读物,永不能达高深之了解。施教之标格日迁就,受教者之智慧日窒塞。此如希腊神话亚侠儿(Achilles)与乌龟赛跑,亚虽善走,将永远赶不上乌龟。何者,亚之脚步如必依照乌龟前行之距离为比例,而不许其痛快大踏步前进,则势惟裹足不前,而乃永无追出乌龟之望。今日中国中小学本国文字文学之课程,皆乌龟也。此种迁就主义,不知埋没冤屈了几许英才。今日中国一中学毕业生,彼乃无自己阅读本国古书之能力。彼乃不啻生在一无文化传统之国家。彼心神之所接触者,仅限于眼前数十年间之思想事物而止。彼之情感何从潜深?意志何从超拔?趣味何从丰博?胸襟何从豁朗?此等教育,大率为目前计,不为文化之传统计。此等教育所造就之人才,除却所谓科学知识外将一无所得。而今日中国中学大学中之教授外国文,则精神意趣,与前所云云者大异。彼尚不失有一标格,而强人以必赴。故即在中学生已有读莎士比亚之戏剧,雪莱之诗歌者。二十年来,各大学中学学生之晨夕孜孜披一卷而高声朗诵者,百分之百皆诵英文,绝无一人焉读本国文学者。若有之,其人必为侪偶所腹诽,所目笑,而彼亦将引为奇耻大辱。然此数十年来,试问国内造就几许真懂莎士比亚雪莱之文学者乎?以中国之大,有千人万人熟读莎士比亚雪莱不为多。独怪以中国之大,乃渐渐有寻不到能读本国文学本国古书之青年之情形。彼辈在中学校毕业,既未具备自己阅读本国文学本国古书之能力,彼之全部精力乃全费于研读外国书之准备。及其毕业以后,所入者乃中国社会,绝少继续研读外国书之机会,而中国文学中国古书虽日触于眼帘,彼固无此能力,亦无此信仰,并无此兴趣。彼乃不得不与学术界文化界相隔绝。即自大学毕业者,亦何独不然。彼辈大率能读外国书,而未必常有外国书可读。彼辈大率不能读中国文学古书,而彼辈终不能耐无书可读之苦。则一般阅读兴趣,乃不得不集中于时下新起之新文艺与宣传小册,以为消遣。故今日中国国内之学术空气,仅能存在于学校之内部,绝无法推广及于社会。而所谓学校内部之学术空气,又常汲源于外洋,非植根于本土。今日中国国家教育,乃尽力自掘传统文化之根,又尽力为移花接木之试验,而二三十年来之成效,则已大可见。若曰推行科学教育,则科学应重事物实验,不应白费学者心血于外国文字文学之研习。若曰推行文化教育,则中国自有传统文化。谓中国无有科学则可,谓中国无文哲史艺诸学则绝不可。谓中国政法经济诸学须参考外国新学则可,谓研究政法经济者可绝不理会中国已往自己传统则绝不可。若曰必全盘西化,则专通英文,决非全盘西化。若强中国人必兼通英法德俄各国文字,其事既难。若亦穷本竟源,先修希腊拉丁文,再从之自创一新式西化之中国文,一若彼中英法德俄诸邦之自十四世纪以下之各自创其新文字然,此又不可能之事也。然则中国学校何以必以研习英文为首务,我无以名之,名之曰模仿之教育。夫亦曰英国人读莎士比亚,我亦读莎士比亚而已。英国人读雪莱,我斯亦读雪莱而已。又知英国人尝舍弃希腊文拉丁文之研习而自创新英文,我斯亦舍弃我之古书古文而已。谓之模仿教育,谁曰不宜。夫曰模仿教育,犹逊辞也。刻实言之,则乃一种次殖民地之教育也。故今日中国国家教育之惟一出路,端在转移此种模仿教育之积习。若使中等学校之青年,于晨光曦微,晚灯煜烨之下,手一卷而高声朗诵者,非莎士比亚与雪莱,而为《论语》《庄子》《史记》陶渊明,则具体而微矣。
今日学校教育有一绝大困难问题曰训育,而中等学校尤甚。夫训教一贯,本非离教而别有所谓训也。今离教而求训,训必无效。教者非以已教,乃以己之所学教。己之所学在《论语》孔子,己之所教亦为《论语》孔子
所教非我之言,乃《论语》孔子之言。学者非欲其尊信我,乃欲其尊信《论语》孔子。由尊信《论语》孔子,乃亦尊信及于我。古语云,师严而道尊。然亦以道之尊而后师可严。又曰尊师而崇道。其实亦以道之崇而后师始尊。今学校以训育问题而牵连及于导师制度,深苦导师之不胜任而难其选。夫师之地位在其所教。若求导师,则中国往古圣哲豪杰,如孔子孟子老聃庄周以来,何啻数千百万,皆导师也。使学者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诵其文,若聆其言,不啻耳提而面命。潜移而默化,心领而神会,则既有教而训随之。今乃一切舍弃,曰此已死之陈人,已死之陈言,不足以为教,然则又孰足以为教?昔日小学校儿童所听古事如孔融让梨,如司马光剥胡桃,凡其所学,即可为训。今日小学校所学,大率乃一只狐狸三个小仙女之类耳。昔日中学生国文课颇读《史记·项羽本纪》之类,今日中学生则只读鲁迅之阿Q正传。昔日青年入学校,其背后尚有家庭父兄之教督。今日则全国家庭父兄皆已自承顽固,再不敢教督其子弟,转望子弟自学校携返新教训以焕发其家庭。故今日之青年,就文化传统言之,彼乃上无千古,下无百世,彼乃一无承续无蕲向之可怜虫也。徒日嬲其旁曰革新,曰创造,曰独立,曰自由。则无怪其日趋于犷獟而无文,桀黠而难教。故今日之教者惟有两途。一则曰为公民当云云,一则曰西洋人云云而已。夫公民仅限于奉公守法,仅限于政治之一角落,固未能渗透及于人生之全部。西洋人云云非不可教,然道听而途说,隔靴而搔痒,实不能深切著明也。今欲指导其成一理想的中国人。苟舍此二者,而为师者自以己意为教,曰我欲云云,则学生群起而哄之。然则将何以为教?曰必本于自己国家民族之传统文化以为教。教育即文化之一部分,今既剿截数千年传统文化,只许就目前当今以为教,是则教育脱离文化而成为无文化之教育,故其教育之收效也特难。青年在学校,已感其无可教,而谓一出学校,便可为国家民族理想需要之人才,此又必不可得之数也。
今再概括言之,则本于国家文化教育人才教育之旨趣,一普通中学生,必以能自己阅读本国已往古书古文为其毕业之起码标准。再本此标准而约略设计普通中学之课程,则关于各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之传授,其课程地位最多不当超过文字文学研习课程之一倍以上。而对于外国文字文学研习之课程与时间,最过亦不当超过对于本国文字文学研习时间之三分之一。犹不尽于此,一面尚当于大学校先培植能胜任愉快之中学国文教师,一面又当自小学校起再厉行改变国文国语迁就教育之通病,而后此新标准始有到达之希望。若论科学教育,则本不必多量注重于文字之研修。今既于普通中学外尽量多设各种独立学院,又国家设立大规模编译馆,尽量翻译外国各部门之重要书籍,而学者中之聪明特秀者,仍得于大学文理学院中精研外国文而为中外兼通之人才。此固于时下所主吸收西洋文学及提倡科学教育两无妨碍。必有此调整,而后中等教育乃有彻底更新之可能。否则就中学而言中学,缚手缚脚,左支右绌,殊无自由发展之余地也。
第7章 谁在保护消费者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社会上,除乞丐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全然靠别人的恩惠生活。”(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页)
我们的确不能靠恩惠而获得我们的饮食——但是,我们能全然靠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吗?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改革家和社会批评家们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利己心将使得卖方去欺骗他们的顾客。卖方会趁机利用顾客的单纯和无知,向他们漫天要价,并把劣等货塞给他们。卖方会哄骗顾客去购买他们不需要的商品。此外,批评家们已指出,假如你对市场听之任之,其结果还会影响到直接受害者以外的人们。它可以影响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饮用的水,我们所吃的食品的卫生。据说,为了保护消费者不受他们自己和贪婪的卖方的侵害,保护我们所有的人不受市场交易所产生的消极的毗邻效应的侵害,市场必须另行予以安排,使其臻于完善。
【译者按:消极的毗邻效应(spilloverneighborhoodeffects)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某甲的行动往往对某乙有不利影响,但又不承担任何责任。比如在同一条河流上,上游的化工厂以邻为壑,它所排出的污水对下游的酿酒厂和水厂会造成危害。】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指出的,对看不见的手的批评是有根据的。问题是,为了克服上述弊病而被推荐或采取的目的在于完善市场的那些安排,是不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精心设计的,或者是不是象我们所常见的那样,对策不会比弊病带来更大的危害。
这个问题在今天特别迫切。十几年前由一系列事件——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维尔对制药工业的调查,以及拉尔夫·纳德对通用汽车公司科维牌汽车“以任何一种速度行驶都不安全”的抨击——所展开的运动,使政府在市场上以保护消费者名义进行的干预,在广度上和性质上都起了较大的变化。
从1824年建立的陆军工兵部队到1887年建立的州际商务委员会,再到1966年建立的联邦铁路管理局,这些机构都是联邦政府为管理或监督经济活动而建立的,它们在范围、重要性和目的方面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几乎所有机构都管理某一行业,对该行业拥有明确规定的权限。至少从州际商务委员会建立以来,保护消费者——主要是其经济利益——已是改革家们公开宣称的目标之一了。
在新政以后,干预的步伐大大加快了——1966年共有三十二个联邦政府机构,其中一半是在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建立起来的。然而干预仍然是颇有节制的,并继续采用分别对各个行业进行干预的模式。1936年设立了《联邦登记册》,记载全部规章制度、申诉和涉及各种管制机构的其他事务,它起初颇为缓慢地,随后就急剧得多地扩大篇幅了。1936年它充其量只有三卷共二千五百九十九页,并在书架上占有空间六英寸;1956年增至十二卷,共一万零五百二十八页,占用书架空间二十六英寸;1966年达到十三卷,共一万六千八百五十页,占用书架空间三十六英寸。
接着,在政府的管制活动方面,出现了真正的迅猛扩展。随后十年里,建立的新机构不少于二十一个。这些新机构不涉及特定的产业,而是包括广阔领域:环境、能源的生产和分配、产品安全、职业保险,等等。除了关心消费者的经济利益,保护他们不受卖方的剥削以外,最近建立的各机构主要关心象消费者安全及其福利一类的事情,保护消费者不仅不受卖方、而且也不受他们自己的侵害。
政府用于所有新老机构的支出迅猛上升——从1970年不足十亿美元,剧升到1979年粗略估计的五十亿美元。物价一般说来大体上翻了一番,但政府上述支出则翻成五倍以上。被雇用于管制活动中的政府官员人数增加了两倍,从1970年的二万八千人增至1979年八万一千人,《联邦登记册》的页数则从1970年的一万七千六百六十页增加到1978年的三万六千四百八十七页,占用书架空间一百二十七英寸,即足足有十英尺的书架。
在这十年中,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变慢了。从1949年到1969年,私人企业全体雇员每一人时的产量——劳动生产率的一个简明而综合的指标——每年增长3%强;其后的十年中,每年增长还不到1.5%;在这十年的末期,生产率事实上是下降了。
为什么把这两种发展联系起来呢?一种发展是与保证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健康,保护洁净的空气和水有关;另一种发展则与我们怎样有效地组织自己的经济有关。为什么这两种好事情会发生矛盾?
答案就是,过去二十年里,无论标榜的目的如何,所有的运动——消费者运动、生态学运动、回到田园的运动、嬉皮士运动、有机食物运动、保护自然环境面貌运动、人口的零增长运动、“小的就是美妙的”运动、反核能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反增长的。它们反对新的发展,反对工业革新,反对加强利用自然资源。为此而建立的一批机构,把沉重的负担强加给一个又一个产业,以满足日益详尽和广泛的政府要求。这类机构阻止了某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并按政府官员规定的方式,要求工业必须把部分资金用于非生产性投资。
到目前为止,其后果是深远的,而且似乎今后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后果。正如大核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有一次说过的:“我们用了十八个月制造第一台核动力发电机;现在要十二年;这就是进步。”对纳税人说来,管制的直接费用,是其总费用中最小的一部分,政府每年用掉的五十亿美元,只是执行各种规章制度给各行各业和消费者带来的开支的很小一部分。按保守的估计,这笔费用一年大致为一千亿美元。这还没有把消费者因买到的商品很少有挑选余地和因价格高昂而遭受的损失计算在内。
政府作用方面的这种大变革,多半是随着公众主张所取得的成就而引起,而能和这种主张匹敌的则是很少的。若想一想什么产品目前令人最不满意并许久以来改进极少,那么,邮政业务、中小学教育、铁路客运业务无疑地会名列前茅。若想一想哪些产品或事业最令人满意并改进最大,那么家用器械、电视机和收音机、高保真度设备、计算机,而且,我们还可以加上超级市场和市郊商店区,将一定会列在那类名单的前列。
劣等货全都是政府的工业或政府管制的工业生产的。优质产品则全为私人企业生产的,这类企业同政府只有少许牵连,或者毫无关涉。然而,公众——或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已被说服相信,私人企业生产劣等货,我们需要有经常保持警惕的政府雇员监督商业机构,不让它们把包装漂亮但是不安全的商品,以过高的价格来欺骗那些不了解内情因而轻易上当的顾客。这种宣传运动进行得如此顺利,以致我们正把极为迫切的生产与分配能源的任务转移到我们提供邮政服务的人的手中。
拉尔夫·纳德对科维牌汽车的抨击,是破坏私人工业品信誉的运动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插曲,它作为一个例子,不仅表明了上述运动的威力,而且也表明了这一运动给人造成了多么错误的印家。纳德抨击科维牌车以任何一种速度行驶都不安全,结果引起公众对一系列商品的质量提出了疑问,政府建立了许多机构来管理商品。大约十年以后,上述机构之一终于对科维牌汽车进行了检验。他们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对比检验了科维牌汽车和其他汽车,并且得出结论:“同检验的其他各种汽车相比,1960—63型科维牌汽车是值得赞许的。”现在科维牌汽车迷俱乐部遍布全国,科维牌汽车已经变成收藏家的对象了。可是对于多数人,甚至见多识广的人说来,科维牌汽车仍然是“以任何一种速度行驶都是不安全的”。
铁路业和汽车工业是个极好的例子,说明受政府管制而免受竞争危害的产业与竞争非常激烈的私人工业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这两个产业部门服务于同一市场,并且基本上提供同样的服务即运输。前一个产业是倒退的,没有效率,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改革,只是内燃机替换蒸汽机。现今由内燃机牵引的货车,比起较早年代由蒸汽机牵引的那种货车,几乎没有区别。客车同五十年以前相比,而今开得更慢,服务更差劲。各铁路公司都在亏损,正在逐渐被政府接管。另一方面,汽车工业在国内外竞争和革新自由的刺激下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推广了一项又一项改革,以致五十年以前的汽车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消费者享受到利益——汽车工业的工人们和股东们也是如此。这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可悲的是汽车工业现在急剧地转变成政府管制的工业。在汽车工业中,我们眼前又出现了象过去那种阻碍铁路进步的状况。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受其自身规律的支配,这些规律不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条例,而是科学的规律。这种干预服从于强制力量,并按照与其创议者或支持者的意图或愿望很少相关的方向进行。我们已经考察了福利活动中出现的这种情况。当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时,不管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管制物价和劣等货的出售,还是为了增进消费者的安全,或者为了保护环境,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每一项干预法令都确立起权力地位。这一权力将怎样运用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运用,与其说取决于最初的创议者的目的与目标,倒不如说取决于那些得以控制上述权力的人们,取决于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州际商务委员会成立于1887年,是通过一场政治运动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机构,这场运动是由自称的消费者的代表——当时的拉尔夫·纳德之流——领导的。该委员会已经历了几代人,已有人对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与分析。它是一个很好的事例,说明了政府干预市场的发展史。
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丛林》揭露了芝加哥各屠宰场和肉店不卫生的状况,作为对随之而来的抗议的回答,最初于1906年建立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也已经历了几代人的时光。除了在规定的范围内起作用外,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还在较早的特定行业的管制型式与较近期的职能或跨行业的管制型式之间起着某种桥梁作用。它之所以能起这种作用,是因为1962年凯弗维尔提出的修正案使它的活动发生了变化。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全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环境保护局,都是管制机构的更现代化型式的范例——跨越行业进行干预,不太关心消费者的经济利益。对上述各机构进行全面的分析远远超出我们的讨论范围,我们只扼要讨论它们如何表现出同州际商务委员会和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所具有的共同趋势,以及它们为将来提出的各种问题。
虽然州和联邦政府对能源的干预是长期的立场,但在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禁运以及随后将原油价格提高三倍以后,这种干预有了量的飞跃。
正如我们将要说明的,假如我们不能依靠政府干预来保护我们这些消费者,我们能够依靠什么,市场采取什么方法来达到这种目的,以及这些方法如何能得到完善?
州际商务委员会
南北战争以后,接着是史无前例的铁路扩张——以1869年5月10日在犹他州普罗孟塔利钉进用黄金铸成的最后一颗道钉为象征,标志着联合太平洋铁路和中央太平洋铁路的接轨和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的完工。不久建成了第二条、第三条、甚至第四条横贯大陆的铁路。1865年已经营业的铁路有三万五千英里;十年以后,接近七万五千英里;到1885年超过了十二万五千英里。1890年已有一千条独立营运的铁路。铁路遍布全国各地,通向每一个偏僻的村庄,横贯整个大陆。美国的铁路线长度超过了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铁路线长度的总和。
竞争在当时是激烈的。其结果,货运和客运运费往往很低,恐怕是全世界最低的。自然,铁路公司人员曾抱怨过“无情的竞争”。每当经济动荡,在经济周期性衰退的一击之下,一些铁路公司便陷入破产并转归其他人,或者干脆关门大吉。经济复苏时,铁路建筑的另一高潮便随之而到来。
当时的铁路公司人员彼此联合,组成联营集团,并按照利润水平确定运费和瓜分市场,试图以此改善他们的处境。令他们沮丧的是,各种协定经常遭到破坏。只要一个联营集团的其他成员不降低运费,任何一个成员就能通过削减运费和从其他成员那里抢走生意而获利。当然,他不能公开削减运费,只能隐蔽行事,要使联营集团的其他成员尽可能长久地蒙在鼓里。于是受优待的托运人得到秘密的回扣,各公司对不同地区或不同商品订有差别费率。运费的削减迟早会为人知道,联营集团也就随之而垮台。
在象纽约与芝加哥这样距离遥远、人口稠密的地区之间的竞争,当时是非常激烈的。托运人与旅客们可以在由不同铁路公司和沟通两地的运河水运公司营运的一些交错的线路中进行选择。另一方面,这些铁路的任何一条较短路段中,例如在哈里斯堡与匹兹堡之间,也许只有一条铁路。那条铁路拥有某种垄断地位,只是容易受到可替代的运输方式的竞争,诸如运河或河流等运输方式。当然,这类铁路总要尽可能利用其垄断地位,收取尽可能高的运费。
一种结果就是,由各短程运输——或者甚至一段短程运输——收取的运费总额,有时大于从两个远距离地点之间的长程运输所收取的全部运费。诚然,没有消费者抱怨长程运输的运费低廉,但是,他们确实抱怨短程运输的运费高昂。同样,在秘密的运费削减战中获得了回扣的、受到了优待的托运人不会有怨言,而那些没有得到回扣的托运人,则对“差别定价”怨声载道。
铁路公司是当时的主要企业。它们的地位非常显眼,相互竞争激烈,同华尔街和东部财团有密切联系,报纸上报道的金融控制和欺诈事件很多都与它们有关。各铁路公司成了天生的靶子,特别是中西部农民们攻击的靶子。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发生的格兰其运动,对“垄断的各铁路公司”进行了攻击。农民们通过绿背纸币党、农民同盟等组织联合起来了。所有这些组织都在议会大厦进行鼓动,要求政府管制货运的费用及活动,并往往取得成功。平民党不仅要求对铁路公司施行管制,而已要求彻底的政府所有制和政府经营,威廉·哲宁斯·布利安是通过平民党而出名的。当时的漫画家们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他们把铁路公司描绘成章鱼,章鱼在扼杀国家,在对国家施加极大的政治影响(各铁路公司确实干过这些事情)。
【译者按:格兰其(grange)指1867年在美国开始成立的协进农民会,即全国性保护农民利益的田庄农民组织。绿背纸币党(GreenbackParty)系1875年成立的美国农业家的政党,它反对当时美国政府的收缩通货政策,争取维持廉价币值,以利于农民清偿南北战争中的负债。农民同盟(Farmers’Alliance)为1882年在美国北部成立的农民组织。平民党(PopulistParty)于1892年在美国成立,针对当时美国政府的通货收缩政策,它标榜自由铸造银币的纲领和一般的反对垄断的方针。】
当反对铁路公司的宣传运动高涨的时候,有些有远见的铁路公司人员认识到,他们能使这场运动转而对他们有利,可以利用联邦政府去执行他们确定价格和划分市场的协定,保护他们不受州和地方政府的侵犯。他们加入改革家的行列,一起支持政府管制,其结果是1887年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建立。
大约过了十年,州际商务委员会才得以充分发挥作用。到那个时候,改革家们已在进行另一场改革运动了。铁路只是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之一。他们已达到了目的,他们只偶尔粗略地查看一下州际商务委员会正在做的事情,而没有很大兴趣去领导铁路公司干更多的事情。对于铁路公司人员说来,情形就完全两样了。铁路就是他们的事业,是和他们有关的头等大事。他们准备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花费在铁路上面。而且,除了他们外,有谁能够充当州际商务委员会的职员并去管理这个机构呢?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利用该委员会去谋取他们自己的利益。
第一任政府专员是托马斯·库利,他多年来是代表各铁路公司利益的律师。他和他的同事们向国会要求更大的管制权力,并且被授予了这种权力。正如克利夫兰总统的司法部长理查德·J·奥尔尼,在州际商务委员会刚刚成立六年的时候给伯林顿和昆西铁路公司董事长、铁路巨头查尔斯·E·珀金斯的一封信中所说的:
在目前州际商务委员会的职能受到各法院限制的情况下,它是或者可以使之成为对铁路公司非常有用的机构。它平息了公众要求政府对各铁路公司进行监督管理的喧闹,而在同时这一管理几乎完全是名义上的。但是,这样的委员会历时愈久,就会愈多地倾向于采取商业和铁路公司对事物的看法。这样,该委员会将变成介于各铁路公司与人们之间的一种障碍,保护铁路的利益免受轻率而粗鲁的立法的侵犯。……明智的办法不是毁灭该委员会而是利用它。
州际商务委员会解决了长程运输或短程运输问题。该委员会做到了这点主要是通过提高长程运输的收费率,使之等于短程运费的总和,你得知这一情况是不会惊奇的。除了顾主以外,人人都高兴。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委员会的权力强大,它开始对铁路公司的各种业务实行日益严密的控制。此外,权力从各铁路公司直接选出的代表那里转移到了人数日多的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手中。可是,这对于各铁路公司没有什么威胁。许多官员都来自铁路行业,他们的日常业务是同铁路人员打交道,因而他们未来发迹的主要希望是同铁路公司联系在一起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货运汽车作为长途运输工具出现时,对铁路产生了真正威胁。州际商务委员会坚决维持了铁路公司异常高昂的货运费率,使汽车货运业得以飞速发展。后一行业是不受管制的,并具有高度的竞争性。拥有购买一部运货汽车资本的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该行业。在要求政府管理铁路公司的运动中,人们提出来的主要理由是:铁路公司是垄断企业,对它们必须加以控制,以阻止它们剥削公众,但这一理由对于汽车运货无论如何是不成立的。要找到比汽车货运业更能满足经济学家的所谓“完全”竞争条件的行业,那是困难的。
然而,上述情况并没有阻止各铁路公司去鼓动要把长途汽车货运置于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管辖之下。并且,铁路公司成功了。1935年的汽车运输法赋予州际商务委员会管理汽车运输业者的权力——以保护铁路公司,而不是保护消费者。
汽车货运重复了铁路的历史。它组成了卡特尔,收费率被固定下来了,线路被划分了。随着汽车货运业的发展,汽车货运业的代表对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取代了铁路公司代表的统治地位。正如保护铁路公司免受货运汽车的侵害一样,州际商务委员会已成为全力保护汽车货运业免受铁路公司以及不受管制的货运汽车侵害的机构。尽管如此,该委员会只不过是把保护其官员的利益掩盖起来罢了。
为了能在各州之间开展运输业务,一个汽车货运公司必须具有州际商务委员会签发的执照,即载明便利公众且属需要的执照。1935年国会通过汽车运输法后,州际商务委员会对一下子提出来的大约八万九千份申请执照的报告书,只批准了大约二万七千份。“从那时以来……该委员会一直非常不愿意批准新商号参加竞争。而且,开业的汽车货运商号的合并与破产,减少了这些商号的数目,从1939年的二万五千多家减为1971年的一万四千六百四十八家。在同一时期,受该委员会管辖的在各城市之间营运的货运汽车运载的吨位数增长了,从1938年的二千五百五十万吨增加到1972年的六亿九千八百一十万吨,增加了二十六倍。”
执照是可以买卖的。“运输量的增加、商号数目的减少以及运费管理局和州际商务委员会对运费竞争的干预。大大增加了执照的价值。”据托马斯·穆尔估计,1972年执照的价值总额介于二十至三十亿美元之间——只有这一数字可以衡量出政府确立的垄断地位的价值。对于拥有执照的人们来说,上述价值构成财富,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说来,却是一种由政府干预所带来的损失,而不是一种生产能力。每种研究都表明,取消州际商务委员会对汽车货运的管制,会使托运人的花费急剧地降低——穆尔估计或许会降低四分之三。
俄亥俄州的一家汽车货运公司,戴顿航空货运公司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它有一张州际商务委员会签发的执照,执照特许它从戴顿运货至底特律。为在其他线路上运货,这家公司不得不从州际商务委员会执照的持有者手里,包括一个连一部货车也没有的持有者手里购买运货权。为取得这种特权,它每年得付出十万美元。这家公司的老板曾试图买下某些线路的执照,但迄今为止没有成功。 该公司的一位名叫马尔科姆·理查兹的顾主说:“非常坦白地讲,我不知道为什么州际商务委员会止步不前,什么都不干。据我所知,这是第三次我们支持戴顿航空货运公司的申请,以便帮助我们省钱,帮助自由企业,帮助国家节约能源。……所有开支最后都要由消费者来付。”
戴顿航空公司的一位老板特德·哈克补充道:“就我个人而言,在州际贸易中没有自由企业。自由企业在我国已不复存在了。你不得不为此而付出代价,而且必须付出十分昂贵的代价。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必须付出代价,而且消费者也得付出代价。”
但是,另一位老板赫谢尔·温默却从另一方面来看问题,他说:“我不想同已经获得州际商务委员会执照的人进行争论,只是想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国,但从1936年州际商务委员开始行动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新成员加入汽车货运业。他们不准新成员进入该行业,不准他们同已营业的那些成员竞争。”
我们推测,这就是我们在铁路人员和汽车货运业务者中间一再遇到的反应:给我们执照或者让我们自行放弃各种规章,行;停止签发执照或者废除政府管制体制,不行。考虑到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上述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让我们再来看铁路问题,政府干预的最终影响目前仍未消失。日渐增多的各种严格的规章,使铁路公司不能作出有效的调整,来同小汽车、公共汽车和飞机争夺长途客运业务。铁路公司再一次求助于政府,这一次是以全美铁路客运系统的形式实行客运国有化。货物运输也实行了国有化。紧接着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触目惊心的破产之后,通过联合铁路公司(Conrail)的创立,东北部的许多铁路货运线路实际上国有化了。至于其他地方的铁路行业,前景也十分相似。
飞机运输重演了铁路运输和汽车运输的历史。1938年成立了民用航空委员会,当时由它管理的国内主要(即干线上的)航空公司为十九家。尽管空运量大大增加,尽管对“方便公众并满足公众需要的执照”的申请极多,但现在国内航空公司的数目却减少了。不过,飞机运输的历史同铁路运输和汽车运输的历史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并非最不重要的原因有:一家大国际航空公司的有胆量的英国老板弗雷德·莱克,成功地削减了横越大西洋航线的运费,以及民用航空委员会前任主席艾尔弗雷德·卡恩的个性与能力——近来在行政和立法两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废除了对飞机运输费的管制。对于某一领域来说,这在摆脱政府控制、争取较大自由方面,是人们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它取得的显著成就——航空公司的低运费和高收入——促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废除了对地面运输的管制。然而,一些强大的势力,特别是汽车运输业中的势力,正在组织反扑,所以到目前为止,废除管制仅有极微小的可能性。
最近,航空业中也出现了长短途运输问题,而且附带着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插曲。航空业中的运费差别正好同铁路行业中的差别相反,短途运费反而比长途运费低。事情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该州的面积很大,设立若干家大航空公司不成问题,它们的飞机可以只在该州境内的航线上飞行,结果它们可以不受民用航空委员会的管制。在旧金山与洛杉矶之间的航线上,各公司激烈竞争,产生了一种州内运费,它比民用航空委员会批准州际航空公司对同样航程收取的运费低得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1年自称为消费者保护人的拉尔夫·纳德,向民用航空委员会提出了关于上述差别的控告。而事有凑巧,在这之前,纳德的一家子公司公布了一份有关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出色分析报告,着重说明了长短途运输的区别对待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关于怎样解决航空公司的问题,纳德几乎不可能抱有任何幻想。正象研究政府管制的学者所预料的那样,民用航空委员会的裁决要求各州内航空公司提高它们的运费,以赶上民用航空委员会许可的运费水平,这一裁决后来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幸亏这一裁决由于法律上的各种细节问题而没有执行,并且可能因废除对航空运费的管制而无效。
州际商务委员会的例子说明了什么是可以称之为政府干预的合乎规律的历史。一种真实的或想象的灾难,要求人们采取某些行动。于是出现了政治联盟,由真诚而高尚的改革家和同样真诚的有关各方所组成。联盟成员的目标(例如对消费者的低价格和对生产者的高价格)虽然互相矛盾,但却被“公众利益“”公平竞争”等漂亮词藻掩盖了起来。该联盟说服国会(或一个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的序言充满了动听的词语,而法律正文则授予政府官员“干某件事”的权力。高尚的改革家们感受到了一种胜利的喜悦,并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新的事业上去。有关的各方则尽力确保上述权力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使用。他们一般都是成功的。成功本身产生了自己的问题,于是通过扩大干预范围来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官员分享利益后,甚至连当初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不再得到好处。最终的结果往往与改革家的目标完全相反,并且一般说来,达不到特殊利益集团的目标。然而,这项政府活动确立得非常牢固,同时,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又与它联系在一起,以致废除原有的立法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新的政府立法被用来对付由过去立法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一个新的循环由此而开始。
州际商务委员会清晰地展示了这些步骤的每一步——从对它的成立负有责任的不同寻常的联盟起,直到因全美铁路客运系统成立而引起的第二个循环的开始。该系统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它在许多情况下不受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管制,因而可以做州际商务委员会不准许单个的铁路公司做的事情。自然,冠冕堂皇地讲,建立全美铁路客运系统的目的是改善铁路旅客运输。这个系统得到了各铁路公司的支持,因为它将允许取消当时存在的许多客运业务。本世纪三十年代出色的和赚钱的客运业务每况愈下,由于飞机和私人汽车的竞争,它变得无利可图了。然而,州际商务委员会却不准许各铁路公司削减客运业务。全美铁路客运系统现在既允许削减客运业务,又对保留下来的那些客运业务予以资助。
假如根本没有建立州际商务委员会而是让市场力量起作用,那么,美国今天就会有一个令人满意得多的运输系统。在竞争的刺激下,铁路行业会取得更大的工艺改革,铁路公司会根据运输量的不断变化对线路进行更为迅速的调整,铁路行业也许会因此而小一些,但效率会更高。旅客运输可能为较少的公众服务,然而车辆和设备则会比现在精良得多,服务也会更为周到和迅速。
同样,由于效率的提高和浪费的减少,汽车货运公司的数目将增加,而运货汽车的数目可能减少。现今的浪费表现在回程放空车,以及州际商务委员会要求一些运输公司采取迂回公路线等方面。汽车运输费用将降低,而服务则更好。凡让领有州际商务委员会执照的公司运送过个人行李的读者,会毫不犹豫地同意上述判断。虽然我们不是商业托运人,但我们猜想他们也会同意上述判断的。
整个运输业的状况会与现在完全不同,也许会更多地采用联合运输方式。近年来,少数赚钱的私人铁路营业项目之一,是同一列火车既运送旅客又运送他们的小汽车。铁道平车运输方式无疑会远为迅速地被采用,而且会出现其他许多联合运输方式。
听任市场力量起作用,很难料想结果会是什么,但这正是让市场力量起作用的主要理由。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用户对某项运输业务的评价不高,不愿为它支付价格,或同意支付的价格不能使提供这项服务的人获得的收入高于他从事其他运输业务可能获得的收入,那么,这项业务就无法维持下去。用户和生产者都不能慷他人之慨,来维持一种满足不了上述条件的服务业务。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与州际商务委员会不同,联邦政府保护消费者的第二项主要措施——1906年通过的食品和药物法——不是起因于对高价的抗议,而是起因于对食品卫生的关心。当时是揭露丑闻的时代,是记者进行调查的时代。厄普顿·辛克莱被一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纸派到芝加哥,去调查牲畜围场的状况。他根据这次调查出版了著名小说《丛林》,他写这部小说本来要引起对工人的同情,但是小说却更多地激起了人们对肉类加工不卫生的愤慨。正象辛克莱当时所说的:“我瞄准的是公众的心,但却击中了公众的胃。”
早在《丛林》这部小说问世并激起公众要求制定有关法律的感情以前,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和全国禁酒协会等组织已经成立了全国食品与药物卫生代表大会(1898年),目的是开展宣传运动,促使国会颁布禁止出售假药的法令。当时出售的大部分假药都掺有大量酒精,因而酒精被当作药品来出售和消费。面对这种情况,禁酒组织怎么能不开展斗争呢。
在这里,特殊利益集团也加入了改革家的行列。肉类罐头厂的老板们“在这一工业的历史中早已意识到,使顾主中毒对他们是无利的,特别是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更是如此,在这样的市场上,消费者可以选择其他厂商的产品。”他们特别担心欧洲各国借口屠宰的牲畜有病,限制从美国进口肉类。他们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一机会,让政府证明他们出口的肉类是无病菌的,而且让政府支付检验费。
另一特殊利益集团是药商和医生,他们通过其职业联合会发表意见。同肉类罐头厂的老板相比,或者同州际商务委员会成立时的铁路公司相比,药商和医生的卷入较为复杂,单纯经济方面的考虑较少。他们的经济利益是明确的:如果专卖药和假药由江湖医生或其他人直接卖给消费者,那将同他们的业务相竞争。此外,药商和医生还从职业上关心现有的各种药品,敏锐地知道那些自称能医百病(从癌症到麻疯病无所不医),但实际上疗效甚少的药品给公众带来的威胁。热心公益的精神同自身利益相一致了。
1906年的法令主要限于检查食品和给专卖药加标签,不过由于偶然的原因而不是事先计划,它也管理处方,这一权力是很久以后才加以运用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前身隶属农业部。大约十五年前,不论是最早的机构还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制药工业都没有多大影响。
1937年年中磺胺问世以前,几乎没有制造出任何值得一提的新药。其后,一个化学家力图使磺胺对不能服用胶囊的病人发生疗效,结果就发生了所谓“特效磺胺”灾难。他所使用的溶剂和磺胺的化合物证明是致命的。悲剧的结局是“一百零八人死亡——其中一百零七名是服用了‘特效药’的病人,一名是畏罪自杀的化学家。”“从上述……经验中,药品制造商认识到了出售这类药物可能担负的责任,因而在投放市场前开始进行安全试验以避免类似事件的重演。”同时他们认识到政府的保护对他们可能是有利的。结果,1938年通过了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令,这一法令把政府管制扩及到广告与商标,并且要求所有的新药品在它们进入州际贸易之前,在安全方面须经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管理局应于一百八十天以内批准或驳回申请。
另一悲剧,即1961—1962年的撒利多迈德事件发生以前,制药工业及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之间具有亲如手足的共生关系。根据1938年法令的规定,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准撒利多迈德进入美国市场,只是医生为作实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用这种药物。当一些报告披露了欧洲的孕妇服用撒利多迈德后生下了畸形胎儿的消息时,就连医生也不能以实验为借口使用这种药物了。继之而来的抗议浪潮冲击了1962年的修正案,这些修正案是参议员凯弗维尔1961年对制药工业的调查引起的。上述悲剧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修正案的攻击矛头。凯弗维尔最初指控的是价格,即价值可疑的药品售价过高——这是关于垄断企业剥削消费者的一般性的抱怨。但国会通过的修正案则把矛头更多地指向质量问题,而不是价格问题。这些修正案“在1938年法令规定的安全检验之上,又加上了功效检验要求,同时取消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处理新药申请书方面所受的时间限制。一种新药只有得到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也就是说只有当它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药品符合1938年法令的安全要求,而且在其未来的使用中可以达到预期效果时,该药品才能在市场上出售。”
1962年的修正案是同下面列举的一系列事件相一致的,它们使政府的干预活动剧增,同时改变了政府干预的方向。这些事件是:撒利多迈德悲剧;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它发动了环境保护运动;以及有关拉尔夫·纳德的“以任何一种速度行驶都不安全”的辩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促进了政府作用的改变,而且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积极主动得多。对于环己基氨基磺酸盐(cyclamates)的禁止以及要禁止糖精的威吓。受到了多数公众的注意,但是,这些决非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最为重要的行动。
在1962年修正案中达到最高点的那些立法目标。没有人会不同意。当然,应该保护公众免受不安全而没有疗效的药品的侵害。然而,也应该促进新药的发展,应该把新药尽可能快地供应给那些能从新药中得到疗效的人。正象常有的情况那样,一项有益的目标同其他一些有益的目标发生了冲突。一方面的安全与谨慎,可能在另一方面意味着死亡。
【按:这个可以靠官方认证协调提供新药的人和试验新药的人的关系。】
重要的问题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管制在协调上述各个目标方面是否有效,是否有更好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已有人详细地研究过这两个问题。当前,已有大量证据表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管制是有损于生产的,它阻止生产和销售有用的药物带来的害处,大于它禁止出售有害的或无疗效的药物带来的好处。
政府管制对新药品的创新率产生了极大影响:1962年以来,每年推广的“新化学物质”的数目下降了50%以上。同样重要的是,对一种新药品说来,得到批准要花长得多的时间,而且,发明一种新药品的费用增加了许多倍。费用的增加是同政府批准时间的拖延有一定的关系。根据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的估计,当时发明一种新药品的费用约为五十万美元,从试制到投入市场约需二十五个月。如果计入自那时以来的通货膨胀率,现在发明一种新药花费一百万稍多一点美元也就够了。但1978年“要使一种新药进入市场,得花费五千四百万美元,需要大约八年的努力”——也就是说所需费用增加一百倍,所需时间增加三倍,而与此相比,一般物价则仅仅上涨了一倍。其结果是,各医药公司在美国已没有力量来为患有罕见疾病的病人发明新药品,它们越来越多地依赖销售量大的药品。长久以来在新药品发明方面居于首位的美国,现在迅速地落到了后面。而且,我们甚至不能从国外发明中得到充分的好处,因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往往不承认国外有关机构对药品性能的鉴定。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同铁路客运一样,对新药发明也实行国有化。
由此而产生的所谓“药品时滞”,表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在药品供应上存在的差异。例如,罗彻斯特大学药品发明研究中心的威廉·沃德尔博士提出的一份详尽研究报告表明,许多在美国买不到的药品在英国可以买到,而在英国买不到的药品在美国同样难于买到,而且在上述两个国家,可买到的药品投入市场所需要的时间,平均算起来在英国要快一些。沃德尔博士在1978年说:
某些很有疗效的药品在美国买不到,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如英国却可以买到,如果调查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许多美国病人正是因为缺乏这些药品在忍受病痛的折磨。例如,有一两种称为贝他——封阻剂(Betablockers)的药品,现在发现它们能防止心脏病患者因突然发病而死亡,也就是说能够防止冠状动脉因心肌梗塞而死亡。假如在美国有这类药品,它们一年中可以拯救上万条生命。在1962年修正案通过后的十年里,医治高血压——即为了控制血压——的药品在美国没有一种得到批准,而英国却批准了好几种。在全部心血管领域,从1967年到1972年的五年期间,仅一种药品得到了批准。这是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组织机构上存在的众所周知的问题相联系的。
与病人有关系的是,治疗方案过去常常由医生和病人来决定,而现在则越来越多地由联邦一级的专家委员会来决定,这些委员会及其上属机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一非常偏重于避免危险,以致使我们常常能够得到较为安全的药品,但却得不到有效的药品。最近我从上述一些咨询委员会那里听到一些值得重视的言论。它们在考虑某些药品的取舍时经常说,“患有如此严重的疾病的人不多,无需在市场上广泛出售这种药品。”如果你努力干的事情,是为了全体居民的利益而把药品的毒性减到最小程度,那是很好的;然而,如果你碰巧是那“人数不多的病人”之一,也就是说你患有一种极为严重的疾病或一种很罕见的疾病,那么你则交了恶运。
假定所有这一切都是事实,那么不让危险的药物进入市场,防止撒利多迈德这种药物引起一系列灾难,能否证明所付出的代价是合理的呢?萨姆·佩尔兹曼根据以往的事实对这个问题作了非常仔细的研究,而且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上述做法的害处大大超过了好处。他解释他的结论部分地是通过指出这一点:“1962年以前,市场使无效药品的卖主受到的惩罚似乎已经足够了,不需要管制机构再来插手干涉。”生产撒利多迈德的各厂家终究支付了几千万美元的赔偿费而收场。这对防止任何类似事件的发生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当然,错误——撒利多迈德悲剧就是一个错误——仍将发生,但将在政府的管制之下发生。
事实证明了一般推论的正确性。尽管愿望是良好的,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实际上阻挠了新的可能有用的药品的发明和销售。
如果你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一名官员,负责审批一种新药品,那就可能犯两种很不相同的错误:
1、批准一种新药品,它具有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即导致大批人的死亡或受到严重损害。
2、拒绝批准一种药物,而这种药物能拯救许多生命或减轻巨大的痛苦,并且没有不良的副作用。
假如你犯的是第一种错误,批准生产撒利多迈德,每家报纸就会在头版刊登你的名字,使你大为丢脸。假如你犯的是第二种错误,谁又会知道呢?知道此事的只有推销这种新药的药商和若干研制这种新药的药剂师和医生。前者会被斥为不顾人民死活的贪得无厌的商人,后者发发牢骚也就没事了。那些生命本来可以得到挽救的人们不可能提出抗议。他们的家人也无从得知心爱的亲人是由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一名素昧平生的官员的“谨慎小心”而丧失其生命的。
销售撒利多迈德的欧洲各医药公司受到了攻击,而不批准在美国使用撒利多迈德的那位妇女(弗朗西斯·O.凯尔西博士,曾由约翰·F.肯尼迪授予一枚政府优异服务金质奖章)则获得了声誉与名望。你究竟更急于避免哪一种错误,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怀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愿望,你或者我,假如处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官员的地位上,一定会趋向于拒绝或推迟批准许多好的药品,以便避免批准一种具有副作用的药品,引来一则值得报道的新闻,哪怕这种可能性很小。
这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因制药工业的反应而加强了。这种倾向导致过分严格的标准。得到政府批准要花更多的钱,要等待更长的时间,要冒更大的风险。研究新的药品带来的好处减少了。各公司不再那么害怕竞争者的研究工作取得新成果。现有各厂商和现有各种药品受到保护不要竞争的影响。新的参加者受到阻挠,研究工作可能集中在争论最小即革新最少的方面。
我们当中一人在1973年1月8日出版的《新闻周刊》上提出,因为上述种种理由,应该取消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后来该刊物收到了药厂工作人员的一些信件,信中谈到了他们自己的一些不幸经历,从而证实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阻碍药品的发明这一断言。但是,大部分人也发表了如下的看法:“和你的意见不同,我认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应该取消,但是我确实认为它的权力应该”这样或那样地加以改变。
其后,以“汪汪叫的猫”为题的一篇文章(1973年2月至9日)答复说:
有人说:“如果猫能汪汪叫,我希望有一只猫。”你对这种人会有什么看法?实际上他的这种说法同你下面的说法是完全一样的:如果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行为符合我的想法,那我将支持它。说明猫的特征的生物学法则,比起说明政府机构在其一旦建立后的活动的政治法则,并不更为严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活动的方式及其有害的后果,并非偶然的原因所造成,也不是人们容易改正的某种错误所造成,而恰好象喵喵的叫声同猫的本能有关系一样,是该管理局成立本身的结果。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你承认不能任意把特征归因于各种化学和生物的实体,不能要求猫发出汪汪的叫声,也不能要求水燃烧起来。那你为什么假定在社会科学中情形是不同的呢?
人们普遍错误地认为,各种社会机构的行为是可以任意改变的。这是多数所谓改革家犯的根本错误。这种错误说明为什么他们如此经常地感到,过失在于人而不在于“制度”;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赶走坏人”,让好人管事。这种错误说明他们的各项改革为什么在表面取得成功时,常会走上歧途。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带来的害处,并不是主管人的无能造成的,除非说人类本身就是无能的。他们大都是有才干的和忠实的公务人员。然而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对主管某一政府机构的人的行为的影响,要比他们对该机构活动的影响大得多。无疑会有例外,但例外是极少的——差不多象汪汪叫的猫那样稀少。
上述情况并不意味着有成效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但是,要使改革成功需要考虑支配政府机构活动的政治法则,而不要单纯责备政府官员效率低、浪费严重,或者怀疑他们的动机,觉得他们没有真正卖劲干活。凯弗维尔修正案改变了对公务人员的压力和刺激,在此之前,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虽然也带来害处,但要比现在少得多。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作为例子说明了管制活动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发生的变化。这个委员会跨越各个产业部门。它关心的主要不是价格或成本,而是安全。它拥有广泛的处理权限,并仅在最一般的授权条件下活动。
1973年5月14日正式成立的上述“委员会,被授予特别权力,保护公众不因消费品具有过大危险而遭受伤害,帮助消费者评价这些产品的安全,制定有关消费品安全的标准,在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把上述标准相互抵触的地方减少到最低限度,并调查研究消费品造成死亡、疾病和伤害的原因及其预防方法。”
该委员会的权限适用于“任何物品及其构成部分,其生产和分配是(Ⅰ)为卖给消费者……或(Ⅱ)为消费者使用、消费或享受”。不属于该委员会管制的是“烟草及烟草制品;汽车及汽车备件;药物;食品;飞机及飞机部件;某些船艇;以及其他一些物品”——所有这些差不多都属于其它管制机构如酒、烟和火器局、全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联邦航空管理局和海岸警备队等的权限之内。
虽然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刚刚建立不久。但它很可能成为一个主要机构,这一机构对我们行将购买的产品和劳务说来,将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于各种产品,从安全火柴到自行车,从儿童们的玩具火枪到电视接收机,从垃圾箱到圣诞树上的小灯泡,该委员会均进行检验并颁布安全标准。
提高产品的安全性显然是个很好的目标,但将为此付出多大代价,又将按照什么标准来衡量安全或不安全呢?“过大的危险”不能说是一个很科学的词,因为我们无法给它下一个客观的定义。对于儿童(或成年人)的听觉说来,火枪发出多大分贝的声响构成“过大的危险”,我们认为火枪的声响有危险,是因为有时看到训练有素而拿高报酬的“专家”在玩火枪时戴着耳套,这根本不能使纳税人相信他们的钱花得是地方。同不够“安全”的自行车相比,一辆“较安全”的自行车可能速度较慢、较笨重又比较昂贵。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在颁布标准时,根据什么尺度来决定自行车的最大速度和应有的重量,根据什么决定应花更多的钱来达到更大的安全?较安全的标准能带来较多的安全吗?还是只会促成使用者不太注意和不太留神,大部分自行车事故和类似的事故毕竟是由于人们的疏忽大意造成的。
大多数这类问题没有客观的答案——可是,在制定和颁布标准的过程中,这些问题无疑必须加以回答。这种回答将会部分地反映有关公务人员的任意判断,偶尔也反映消费者或消费者组织的评价,他们碰巧对有关产品具有特殊兴趣,然而多半是反映产品制造者的影响。一般说来,只有产品制造者对拟议的标准具有浓厚的兴趣,能够发表有见解的意见。的确,制定产品标准的工作大部分已移交绘了各同业公会。毫无疑问,制定的标准将增进同业公会成员的利益,特别是保护他们不受国内外可能出现的新生产者的竞争。结果将加强现有的国内工厂主的竞争地位,使得研制新产品和改进老产品花费更大,困难更多。
当产品按照事情的正常发展进入市场时,就有机会进行反复的试验。无疑,会生产出劣等产品,会犯错误,会出现意料之外的缺点。但是,所犯的错误通常是小错误——不过也有一些大错误,如最近生产的燧石500号涂料车胎——而且可以慢慢纠正。消费者可以亲自进行试验,看自己喜欢哪些产品,不喜欢哪些产品。
当政府通过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介入时,情形就不同了。在产品得到广泛试用和在实际使用中出差错之前,必须作出许多决定。产品的标准不能适应于不同的需要和爱好。它千篇一律地对待一切需要和爱好。消费者将不可避免地失去试验一系列可供选择的产品的机会。仍然会犯错误,一旦犯错误,就是大错误。
与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有关的两个事例可说明这一问题。
1973年8月,该委员会刚刚成立三个月,“就宣布某些牌子的雾喷粘胶剂具有直接的危险,禁止人们使用。该决定主要是根据某研究机构的一位研究人员的初步发现,这位研究人员认为粘胶剂会使孕妇生下有缺陷的孩子。由于更为彻底的研究无法证实最初的论断,该委员会在1974年3月解除了禁令。”
这样迅速地承认错误是值得大加赞许的,并且对于一个政府机构说来是极其难得的。但最初的决定已经带来了危害。“看来至少有九名使用过雾喷粘胶剂的孕妇,做了人工流产,对该委员会的初步决定作出了反应。她们害怕生下有缺陷的孩子,因而决定停止怀孕。”
一个严重得多的事例是所谓特里斯(Tris)化学药品事件。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成立后,负有实施1953年通过的“易燃纺织品法令”的责任,该法令企图减少因产品、纺织品及有关原料意外燃烧而引起的死亡与伤害。该委员会的前身于1971年颁布了有关儿童睡衣睡裤的安全标准,这一标准在1973年年中被该委员会固定了下来。当时达到这一标准的最经济的方法是把一种名叫特里斯的能防止燃烧的化学药品换进布料中去。不久,在美国制造和销售的儿童睡衣睡裤约99%含有特里斯。后来发现这种化学药物是一种很厉害的致癌物质。1977年4月8日,该委员会宣布禁止在儿童服装方面使用这种化学药品,并且要求从市场上收回用这种化学药品处理过的服装,要求消费者退货。
不用说,该委员会在其1977年年度报告中,并没有承认正是它以前的行动造成了这种危险局面,没有承认它对此应负的责任,而是装出一副面孔,好象是它发现了这一问题,现在正由它来加以解决。最初的要求使千百万儿童面临得癌症的危险。最初的要求和其后禁止使用特里斯,两者都把大量费用强加给生产儿童睡衣睡裤的厂商,归根到底,意味着把费用强加给顾客们。可以说,最终一切费用都要落在顾客头上。
这个例子有助于说明全面管制和市场交易之间的区别。要是当时允许市场发生作用,某些制造商无疑也会使用特里斯,使其产品具有抗燃性,从而增加对顾客的吸引力,但采用特里斯的进程将是缓慢的。在大规模采用这种化学药品之前,人们会发现它的致癌性质,因而停止使用。
环境
环境保护是联邦干预活动发展得最迅速的领域之一。1970年为“保护和改善物质环境”而建立的环境保护局,被赋予日益增大的权力与权限。它的预算从1970年到1978年增加了六倍,现在超过了五亿美元。它拥有大约七千名职员。为了使环境符合它规定的标准,该局每年向工业部门以及地方和州政府征收几百亿美元的费用。目前,在企业新的资本设备净投资总额中,大约有十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用于防止污染。这还未算入由其他机构征收的必要费用,如旨在控制机动车废气的费用,或是土地利用规划或荒地保持的费用,或是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为保护环境而进行的大量其他活动的费用。
保护环境和避免过度污染是现实问题,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当一种行为的全部代价和利益,以及受害者或得益者易于分辨时,市场可以非常有效地确保人们只采取这样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对所有参加者来说,利益大于代价。然而,当代价和利益或者受影响的人不好分辨时,市场就会失灵,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说过,这是“第三方”或毗邻效应造成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某一个住在上游的人污染了河水,他实际上是用脏水去同下游的人交换好水。下游的人很可能愿意根据某种条件进行交换。问题是,不可能使这种交易成为自愿的交易,不可能辨认出谁得到了应由上游某人负责的脏水,而且不可能要求居住在上游的人事先征得居住在下游的人的同意。
政府是一种手段,通过它我们可以弥补“市场的失灵”,可以根据我们的意愿较为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生产出所需要的清洁的空气、水和土地。不幸的是,导致市场失灵的那些因素,也同样使政府难以找到一种满意的解决办法。一般说来,政府同市场参加者相比,前者并不能比后者更容易地辨认出谁是受益者谁是受害者,也不能更容易地估计出上述两种人各得到多少好处受到多少害处。利用政府来补救市场的失灵,常常只不过是以政府的失灵代替市场的失灵。
公众在讨论环境问题时,常常是感情多于理智。在许多讨论中,好象问题是要么有污染,要么没有污染,似乎应该而且可以有一个没有污染的世界。这显然是毫无意义的空想。凡严肃思考过这一问题的人,都不会认为应该使或可以使世界没有污染。我们可以不让汽车污染空气,例如,只消废弃一切汽车就行了。但这却使我们无法享受现在已享有的工农业生产力,从而使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置许多人于死地。大气污染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大家呼出的二氧化碳。我们可以非常简单地终止这一状态。但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正象得到我们需要的其他好东西要付出某种代价一样,得到清洁的空气也是要付出某种代价的。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因而必须权衡减少污染带来的好处和付出的代价。而且,“污染”不是一种客观现象。对一个人来说是污染,对另一个人来说则可能是享乐。对于我们当中某些人来说,摇摆舞音乐是噪音污染;对于我们当中另一些人而言,却是一种享乐。
实际的问题不是“消灭污染”,而是用什么方法能够使污染量“适当”,“适当的”污染量的意思是:减少污染得到的好处刚好大于为了减少污染我们必须放弃其他好东西(如房屋、鞋子、上衣等等)而作出的牺牲。如果我们做得过分,牺牲就会大于得到的好处。
妨碍我们合情合理地分析环境问题的另一个障碍是,人们往往从善与恶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似乎有一些怀有恶意的坏人心肠很黑,是他们把污染物送入大气中的,因而这是一个与动机有关的问题,只要我们当中那些高尚的人愤怒地起来制服这些坏人,一切就会好起来。骂人总是比有理智而艰苦细致地分析问题要容易得多。
就污染说来,被指责的魔鬼往往是“工商企业”,即生产商品和劳务的企业。事实上,对污染负有责任的人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可以说,消费者造成了引起污染的需求。对于从发电厂的烟囱冒出来的烟尘,用电的人是应该负责的。假如我们想得到只带来少量污染的电,我们将直接或间接支付很高的电费,使之足以补偿额外的费用。获得比较清洁的空气、水和其他一切所支付的费用,最终必须由消费者负担。没有人会为此付款。企业只是一种媒介,借以协调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活动。
因为控制污染和保护环境带来的好处和造成的损害往往落在不同人身上,所以问题大大复杂化了。例如,从荒地利用面积的增加,从江河湖泊环境的改善,或者从市内空气污染物的减少等方面得到好处的人,通常和那些因为食品、钢铁或化学制品的成本增加而受到损害的人不是同一类人。我们一般的感觉是:因减少污染而得益最多的人,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教养上,都比因允许较多的污染,从而使物品的成本较低而得益最多的人要强。后一种人宁愿要较便宜的电力,而不要较清洁的空气。董事规则在控制污染方面仍然起作用。
总的说来,政府在控制污染方面采用的方法,同政府在管理汽车运输、管理食品和药物以及增进产品安全等方面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为控制污染,建立了一个拥有处置权力的政府管制机构,该机构颁布了私人企业、个人以及州和地方团体必须遵守的各项规章制度。由上述机构和各级法院确保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
这种控制污染的方法不能有效地确保成本与收益相等。由于完全靠强制命令的方法解决问题,这种方法造成的局面是,谁违反规定谁受惩罚,而不是买与卖;是对与错,而不是多与少。而且,它具有和其他领域中的管制方法相同的缺点。受管制的人或机构卖力去做的,不是花费人力物力达到政府规定的标准,而是对政府官员施加影响,以获得对他们有利的规定。另外,管制人员的自身利益同保护环境的基本目标关系极少。正如官僚统治下的一般情况那样,广为分散的个体利益受到漠视,集中起来的利益则备受照顾。过去,所谓集中起来的利益一般是指商业企业,特别是规模巨大、有权有势的企业。最近,除大企业外,又增加了一些组织得很好、自称代表“公共利益”的集团。这类集团自称代表某些顾客的利益,而顾客可能对它们的存在一无所知。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和现有的专门的管制与监督方式相比,一种有效得多的控制污染的方法是对排出物征收费用,让市场规律起作用。举例来说,可以对排出的每单位废物征收特定数额的税款,而不是要求各厂商建立专门处理废物的工厂,也不是要求它们排入江河湖泊的水必须达到特定的标准。这样一来会刺激厂商采用最经济的方法减少排出物。同样重要的是,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客观地衡量出减少污染的费用。如果低额税率导致污染大量减少,那将明确告诉我们,允许排出污染物几乎得不到什么好处。另一方面,如果征收高额税仍有大量污染物排出,那将表明相反的情形,但高额税将提供足够的金额赔偿受损失的人或者消除损失。税率本身应随着费用和收益的变化而变化。
和管制一样,废物排出税将自动地把费用加到对污染负有责任的产品使用者身上。那些减少污染花费大的产品,相对于减少污染花费小的产品,价格将上升,正如现在那些因管制活动而被征收重税的产品相对于其他产品价格上升一样。前一类产品的产量将上升,后一类产品的产量将下降。废物排出税和管制之间的区别在于:废物排出税将以较低的费用更有效地控制污染,而且给不造成污染的活动带来的负担较少。
A·迈里克·弗里曼第三和罗伯特·H·哈夫曼在一篇出色的文章中写道:“我国不采用经济刺激的方法,是因为该方法行之有效,这样说并非完全开玩笑。”
正如他们所说的,“结合环境质量标准建立污染税制度,会解决有关环境方面的大部分政治冲突,而且将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解决这些冲突,让这一政策的受害者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决定政策的人们力图避免的正是这种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作风。”
上面我们非常简要地论述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影响深远的问题。最后我们指出这样一点也许就够了:在政府根本不应发挥作用的领域中——如在汽车货运、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的价格确定及线路分配中——政府管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在政府应发挥某种作用的领域中也出现了。
建立污染税制度也许还会导致人们重新看待市场机制在某些领域中的作用,在这些领域中,人们一般认为市场机制起的作用是不理想的。毕竟,不理想的市场可能和不完善的政府干得一样好,或者更好一些。在控制污染方面,重新看待市场机制的作用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假如我们看一看现实而不是书本上的词句,那么同一百年以前相比,今天的空气一般说来要清洁得多,水也比较卫生。现在,比起落后国家,在世界先进国家中空气较为清洁,水也较为卫生。工业化产生了新的各种问题,但是它也提供了解决一些重要问题的手段。汽车的发展确实增加了一种污染形式——但它却基本上结束了人们更不喜欢的一种污染形式。
能源部
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美国实行禁运,引起了一连串能源危机,并且,加油站不时发生排长队的现象,从那时起,能源问题一直使我们很伤脑筋。政府的反应是成立一个又一个的官僚机构以控制和管理能源的生产及使用,最后是在1977年成立了能源部。
政府官员、报纸报道和电视台时事评论员,都把能源危机的原因习惯性地归之于贪婪的石油工业,或者浪费的消费者,或者恶劣的气候,或者阿拉伯的酋长们。但实际上,它们对能源危机都没有责任。
石油工业毕竟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期了——并且它一向是贪婪的。消费者不会突然变得浪费起来。我们过去也有严酷的冬天。早在人类有史以来,阿拉伯酋长们就已经在追求财富了。
那些用上述愚蠢的解释来充塞报纸和广播的、精明而老练的人们,似乎从来没有自问过 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1971年以前的一个多世纪中(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为什么没有能源危机,没有汽油短缺,没有关于燃料油的问题。
能源危机是政府造成的,当然,不是故意造成的。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位总统从来没有致函国会要求制定带来能源危机和使人们排长队买汽油的法案。但是既然说到问题的一方面,就得说另一方面。自从尼克松总统1971年8月15日冻结工资和物价以来,政府就对原油、零售汽油以及其他石油产品强行规定了最高价格。令人遗憾的是,取消对所有其他产品的最高价格时,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把原油价格提高了三倍,这阻碍了美国取消对石油及其产品的最高价格。对石油产品规定最高法定价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1971年以来的时期共有的关键性因素。
经济学家们不可能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即如何造成产品过剩和产品不足。你想使产品过剩吗?让政府通过法律规定最低价格,并让这一价格高于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流行的价格。我们曾多次采用这种方法使小麦、食糖、奶油和其他许多农产品过剩。
你想要产品不足吗?让政府通过法律规定最高价格,并让这一价格低于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流行的价格。这就是纽约市以及最近其他城市对出租的住宅做过的事情,并且,这也是所有这些城市正在遭受或即将遭受房荒之苦的原因。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种产品短缺的原因,也是现在出现能源危机和汽油短缺的原因。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在明天结束能源危机和汽油短缺——我们指的是明天,不是今后六个月,不是今后六年。那就是废除对原油和其他石油产品的一切价格管制。
政府的其他错误政策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垄断行为,可以继续使石油产品保持高昂的价格,但不会产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四分五裂、一团混乱的局面。
或许令人惊奇的是,上述解决办法会降低消费者的汽油费用,我们说的是真实的费用。油泵中每加仑汽油的价格可能要上涨几美分,但消费者不用再为排长队和寻找有油的加油站浪费时间和汽油,也不用再为能源部的年度预算付款了。能源部1979年的预算达一百零八亿美元,或每加仑汽油大约九美分。
为什么这种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法没有被采用呢?就我们所见,是由于两个基本原因——一个是一般的原因,另一个是特殊的原因。使每一个经济学家失望的是,要使除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外的大多数人了解价格制度是如何起作用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新闻记者和电视台时事评论员似乎特别反对他们在大学一二年级学过的那些基本原理。其次,废除价格管制会使真相大白,告诉人们能源部二万名雇员的活动是多么无益,多么有害。有人甚至可能会想:要是没有成立能源部该有多好。
卡特总统宣称,政府必须实施一项生产合成燃料的庞大计划,否则到1990年我国的能源将被耗尽。这一主张又怎么样呢?这也是一种神话。政府计划似乎是一种解决办法,这仅仅因为政府处处阻止采用有效的自由市场解决办法。
根据长期合同,我们付给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每桶石油大约二十美元,在现货市场(立即交货的市场)上,我们所付的价格甚至高于此数,可是政府却迫使国内生产者按每桶五点九四美元的低价出售石油。政府对国内生产的石油征税,用以补助从国外进口的石油。我们付给从阿尔及利亚进口的液化天然气的价格,比政府允许的国内天然气生产者所收的价格,要多出一倍以上。政府把严厉的有关环境方面的要求强加给能源使用者和生产者双方,而极少或者毫不考虑经济上所包含的费用。复杂的规章制度和拖拉的官僚作风,大大拖长了兴建以原子核、石油或煤炭为燃料的发电厂所需要的时间,拖长了充足的煤炭供应量进入生产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并且成倍地增加了成本。政府的这种不利于生产的政策,扼杀了国内的能源生产,使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依赖外国的石油——尽管卡特总统说过:“依赖于一条几乎环绕整个地球的、靠不住的油船运输线是很危险的。”
1979年年中,卡特总统提出了一项为期十年、耗资八百八十亿美元的生产合成燃料的庞大政府计划。让纳税人为产自油页岩的每桶石油直接地或间接地花费四十或更多的美元,而同时却禁止国内油井所有者从某些类别的石油中每桶收取五点九四美元以上,这果真有道理吗?或者,象爱德华·J.米切尔在《华尔街日报》(1979年8月27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要问……就算我们花费八百八十亿美元能在1990年生产出一些每桶定价四十美元的合成石油,这又怎么能够使我们不论在今天还是在1990年不依赖石油输出国组织每桶定价二十美元的石油呢?”
从油页岩、含油砂层等等提炼燃料是有意义的,如果把所有的费用都考虑进去之后,这种方法生产能源比各种替代办法更便宜的话。市场是决定上述方法是否便宜的最有效的机制。如果这种方法较为便宜,那么私人企业开发这些替代资源就将是有利的——只要它们获取利益同时负担费用。
只要私人企业相信将来的价格不受管制,它们就可以指望获取利益。否则私人企业就等于是在打一场“反正我都输”的赌。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假如价格上涨,管制及“暴利税”会赫然出现;假如价格下跌,私人企业就要两手空空。这种前景削弱自由市场,并使卡特总统的社会主义政策成为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案。
只要要求私人企业为破坏环境而付款,它们就将负担所有的费用。执行这一政策的方法是对排出物征收捐税,而不是让某一政府机构任意制定各种标准,随后又建立另一个机构来杜绝前一个机构的官僚作风。
对于私人企业发展各种替代性燃料说来,价格控制和管制的威胁是唯一重要的障碍。据说发展替代性燃料风险太大,资本费用太多。这完全错了,冒险正是私人企业的本质所在。把风险强加给纳税人而不是资本家,并不能消除风险。阿拉斯加输油管表明,私人市场可以为有前途的工程筹集巨额资金。打发税务员征税,并不能增加国家的财力,增加国家财力的方法是让证券市场发挥作用。
不管怎么说,我们人民将要为我们所消费的能源付钱。假如我们直接付钱,并能够自己决定怎样使用能源,而不是通过纳税和通货膨胀间接付钱,也不是由政府官员告诉我们怎样使用能源,那么,我们为所消费的能源支付的总金额将会少得多,得到的能源将会多得多。
市场
这个世界不是尽善尽美的。永远会有质量低劣的各种产品、庸医和诈骗能手。但总的看来,如果允许市场竞争起作用,那它同强加到市场头上的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相比,将能更好地保护消费者。
正象亚当·斯密在本章开头我们引用过的那段话中所说的,竞争保护消费者不是因为商人比官僚们心肠软,不是因为商人有更多的利他主义思想,或更慷慨大方,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有才能,而只是因为为消费者服务正是为他们自己的私利服务。
假如一个店主向你出售的商品比其他店主出售的商品质量低或价格高,你就不会继续光顾他的商店了。假如他买来供出售的商品不合你的需要,你就不会购买。因此,商人们在全世界搜购可能适合你的需要并受你欢迎的各种产品。而且他们极力推销购买来的商品,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会垮台。你走进一家商店,没有人强迫你买什么。你可以随便买哪一样东西或者到另一家商店去。这是市场和政治机构之间的基本区别。你能自由选择。没有警察从你口袋里掏钱去为你不想要的某样东西付款,没有警察要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
然而,鼓吹政府管制的人会说,如果没有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怎么能阻止企业出售搀了假的或者有危险的产品呢?正如特效磺胺、撒利多迈德以及其他许多不太为人所知的事故所表明的,出售这类产品代价是非常高昂的。这是一种非常卑劣的做生意的手法——不是招揽忠实而可靠的顾客的方法。当然,如果没有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会出现各种差错和事故,但正如特里斯事件所表明的,政府管制并不能阻止事故的发生。区别在于犯严重错误的私人企业可能垮台,而犯严重错误的政府机构则很可能因此而得到更多的预算。只要无法预测不利情况的出现,就肯定会出现一些差错和事故,但同私人企业相比,政府并没有更好的方法来预测不利情况。防止差错和事故的唯一方法是停止前进,但停止前进也就消除了出现意想不到的有利情况的可能性。
鼓吹政府管制的人还会说,没有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消费者怎么能判断各种复杂的产品的质量呢?市场的回答是消费者无须自己作出判断。他有一些可以依赖的对象,其中之一就是中间人。例如,百货公司的主要经济职能是根据我们的利益检查质量。我们购买的东西很多,一个人不可能对所有东西都懂行,即便是衬衫、领带或鞋子等最平常物品,我们有时也不能正确地判断其质量。如果我们买了一件不好的东西,我们多半会退给出售商品的零售商,而不会退给工厂主。在判断产品质量上,零售商所处的地位远比我们优越。同百货公司一样,娄巴克·西尔斯公司和蒙特文梅里·沃德公司不仅是销售机构,而且是为消费者有效地检验和证明产品质量的机构。
另一种可以依赖的市场手段是商标的声誉。通用电气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都要获得生产安全可靠的产品的声誉。这是它们“信誉”的源泉,作为一家公司这种信誉甚至比厂房设备更有价值。
还有一个手段是私人检验组织。这样的检验组织在工业部门中是很普遍的,并在证明大量产品的质量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消费者来说,有象消费研究会一类的私人组织,该研究会创立于1928年,并仍在它每月出版的《消费研究》杂志上评价各种各样的消费品;还有1935年建立的消费者联合会,它出版《消费通讯》。
消费研究会和消费者联合会都很成功,有充足的资金雇用大批人员,其中包括工程师以及经过训练的检验人员和办事人员。可是,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它们至多只能吸引1%或2%的可能的追随者。这两个组织中规模较大的消费者联合会现在拥有大约二百万名会员。它们的存在是市场对消费者需求的一种反应。它们的规模很小,而且没有出现其他类似的机构,这表明只有少数消费者需要这类机构,并愿意为它们提供的服务付钱。大多数消费者一定正在从其他方面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指导,并愿意为此支付费用。
有人宣称消费者会被广告牵着鼻子走,这一论断怎么样呢?正如许多耗资巨大的广告宣传的可耻失败所表明的,我们的回答是消费者不会被广告牵着鼻子走。埃德塞尔牌汽车是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一种最不受欢迎的汽车,但该公司却开展大规模的广告宣传运动推销这种汽车。从根本上说,广告是做生意的一种成本,企业家都想从付出的钱中得到最大的好处。设法满足消费者真正的需要和愿望,比起试图制造人为的需要和愿望,不是更为合理吗?的确,同制造人为的需要相比,向消费者出售满足他们现有需要的商品,一般是比较便宜的。
一个极好的例子是所谓人为制造出来的要求改换汽车型式的愿望。可是,尽管开展了耗资巨大的广告宣传运动,福特汽车公司终究没能使埃德塞尔牌汽车成为畅销货。市场上总是有一些不经常改换型式的小汽车,如美国制造的苏珀巴牌小汽车(这种汽车是奇克牌出租汽车的仿制品)以及许多外国小汽车,但它们所能吸引的顾客一直不过是很少的百分之几而已。如果不经常改换型式的汽车是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则制造这种汽车的公司就会兴旺起来,同时其他公司也会仿效它的做法。多数批评家反对广告宣传,不是因为广告宣传操纵嗜好,而是因为一般公众具有浮华庸俗的嗜好——即同批评不一致的嗜好。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光凭想象下结论,应该对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进行一番比较。即要货比货。如果商业广告是骗人的,那么,不要广告或者政府对广告加以控制,是否更为可取呢?至少私人商业方面有竞争,你登广告,我也可以登广告,而一牵涉到政府,就比较难于做到这一点了。政府也从事广告宣传。政府拥有数以千计的与公众联系的代理人,他们用最动听的语言介绍政府的产品。同私人企业的广告宣传相比,政府的广告宣传更加骗人。我们只要看一看财政部为出售其储蓄债券进行的广告宣传就够了。美国财政部为了出售储蓄债券特地印制了一种宣传卡片,由各家银行分发给广大顾客,上面印有以下引人进行储蓄的话:“美国储蓄债券……多么伟大的储蓄方式!”可是,在过去十几年里,凡购买储蓄公债的人都上了当。他在公债到期所得到的金额,同他购买公债所付出的金额相比,只能购买较少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他还得为不利的“利息”纳税。所有这一切是通货膨胀造成的,而通货膨胀则是向他出售债券的政府造成的。然而,财政部却继续散发上述宣传卡片,为储蓄债券做广告,宣称储蓄债券可以“增进个人安全”,是“自行增值的礼物”。
有人说垄断的威胁导致了国会颁布各项反托拉斯法令,这种说法怎么样呢?垄断的确是一种威胁。消除这种威胁的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在司法部下面设立更为庞大的反托拉斯机构或者给联邦贸易委员会拨更多的款。而是废除阻碍国际贸易的各种现有的关卡。这样,来自全世界的竞争将比各项反托拉斯法令更有效地削弱国内的垄断。英国的弗雷德·莱克无须从美国司法部取得帮助以破坏航空公司的卡特尔。日本和西德的汽车制造商迫使美国的汽车制造商生产较小型的轿车。
对消费者的最大威胁是垄断——不论是私人的还是政府的垄断。保护消费者的最有效方法是国内的自由竞争和遍及全世界的自由贸易。要想使消费者不受单一的卖主的剥削,就必须有另外的卖主,消费者能向他购买,而他也渴望卖东西给消费者。在保护消费者方面,可供选择的供应来源要比全世界所有的拉尔夫·纳德之流有效得多。
结论
“流泪的日子即将过去。贫民窟将只是昔日的回忆。我们将把牢房变成工厂,使监狱变成仓库和粮仓。男人将挺起胸膛,妇女将面带微笑,孩子将又蹦又跳。地狱将一去而不复返。”
著名的福音传教士和禁酒运动的领导人比利·森代,就是以上面一段话迎接1920年禁酒运动的开始的。这场运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人们突然发现真正的道德标准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它清楚地告诉我们,目前的道德觉醒,即目前开展的保护大家不受自身侵害的运动将向何处发展。
禁酒运动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开展起来的。酒是一种危险物。每年饮酒过度而丧生的人数,往往超过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管制的所有危险物毒死的人数。但是,禁酒运动究竟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结果是谁喝酒谁就犯有违反国家法令罪,而不得不建造新的牢房和监狱收容罪犯。艾尔·卡彭及巴格斯·莫兰得以横行一时,他们谋财害命,敲诈勒索,抢劫禁卖的酒,并且非法酿酒卖酒。那么,谁是他们的顾客?谁买他们非法供应的酒呢?一些令人尊敬的公民买他们的酒,他们虽然决不会赞同或参与艾尔·卡彭及其同伙干的那种罪恶勾当,但他们却想喝一点酒。为了喝上一点酒,他们不得不违反法律。禁酒运动没有能阻止人们饮酒。它只是使许多在其他方面遵纪守法的公民变成了违法者,给饮酒这件本来很平常的事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从而吸引了许多青年人。它压制了许多具有制裁作用的市场力量,这些力量通常可以保护消费者不受质量低劣的、弄虚作假的以及有危险的产品的损害。它腐蚀了监狱看守,并使道德风尚败坏。它并没有阻止酒的消费。
在禁止使用环己基氨基磺酸盐、滴滴涕和莱特里尔方面,我们目前还远远没有造成上面那种状况。可是,我们正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在被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禁止出售的药物方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半黑市;人们已开始到加拿大或墨西哥购买他们在美国不能合法买到的药品,正象禁酒运动期间人们为了得到一点合法的酒所做的那样。许多认真负责的医生感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要么使用解除病人痛苦的药品而违反法律,要么不使用这种药品而严格遵守法律。
如果我们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最终将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政府有责任保护我们不受危险物的侵害,那么根据逻辑推理,势必要禁止人们饮酒和吸烟。如果应该由政府保护我们在骑自行车和玩火枪时免遭危险,那么根据逻辑推理,势必要禁止悬式滑翔、骑摩托车和滑雪等更加危险的活动。
甚至主管各管制机构的人想到这种前景,也会不寒而栗。就我们其余的人说来,公众对于控制我们行为的更为极端的尝试——如要求汽车安装连锁安全装置以及提议禁止生产糖精等——的反应,充分证明我们丝毫也不需要这种政府控制。假如政府真的掌握一般人无法得到的、有关我们咽下的东西或我们从事的活动的优缺点的情报,那政府应该提供给我们这方面的情报。但政府最好还是听任我们自由选择,让我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本节内容概述
假如政府真的掌握一般人无法得到的、有关我们咽下的东西或我们从事的活动的优缺点的情报,那政府应该提供给我们这方面的情报。但政府最好还是听任我们自由选择,让我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纠正外部性的公共政策:
可交易的许可证如排污
License tradable
治污成本最低的企业会承担最大的减排份额
拍卖许可证
第8章 谁在保护工人
过去两个世纪里,在美国和其他经济上先进的社会里,普通工人的状况有了极大改善。今天,在上述社会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人从事那种繁重不堪的劳动,这种劳动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是常见的,而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现在仍然是不足为奇的。工作条件得到了改善;工作时间也缩短了;享受假期和其他小额优惠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收入大大增加,使普通家庭得以享有早些时候只有少数富人才能享有的生活水平。
如果进行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向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促使全体工人状况得到改善的原因是什么?”多数人的回答很可能是“工会”,其次是“政府”——尽管作出“没有任何原因”或“不知道”或“没看法”的回答的人也许比前两种人要多。可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证明,这些回答都是错误的。
在大部分时期中,工会在美国并不重要。直到1900年,全体工人中只有3%是工会会员。甚至在今天,工会会员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仍然不到四分之一。很显然,工会不是促使美国全体工人的状况得到改善的主要原因。
同样,在“新政”以前,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是最低限度的。政府所起的必不可少的作用,是保护自由市场的正常活动。但是,很显然,直接的政府行动不是促使全体工人的状况得到改善的原因。
至于有人说工人状况的改善“没有任何”原因,当前工人的状况正好证明这样回答是错误的。
工会
滥用语言的最惊人的事例之一是把“劳方”看作是“工会”的同义词——例如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词句:“劳方反对”某某提案,或“劳方”的提案如何如何。这是双重的错误。首先,在美国四分之三以上的工人不是工会会员。甚至在英国,那里的工会长期以来远比美国的工会强大,大部分工人也不是工会会员。其次,把“工会”的利益及其成员的利益等同起来是错误的。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多数工会与其成员的利益是有联系的,而且联系密切,但有许多事例表明,工会头头常常利用合法手段或非法手段如滥用和私吞工会基金,牺牲工会会员的利益而为自己谋私利。这警告我们不要不自觉地把“工会”的利益同“工会会员”的利益等同起来,更不用说把工人整体的利益与工会的利益等同起来。
语言的这种滥用现象是由于过高估计工会的影响和作用而产生的。工会的行动是看得见的,并且是有新闻价值的。它们常常成为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晚间的电视节目也常常不加删节地加以报道。而决定美国大多数工人工资的“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亚当·斯密语),则不那么容易被人看到,也不大引起注意,其结果是讨价还价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
语言的上述滥用也导致了这样的信念,即工会是现代工业发展的产物。事情决非如此。实际上,工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以前的时期,追溯到封建时期城市和城邦内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特有组织形式,即行会。的确,现代工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更为遥远的年代,追溯到大约二千五百年前希腊的医生之间达成的协议。
公认的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于西元前460年左右出生在希腊的科斯岛上,该岛距离小亚细亚海岸只有几英里之遥。当时,科斯岛是一个繁荣的岛屿,已经是医学中心。在科斯岛上研究医学之后,希波克拉底遨游远方,他作为医生,特别是因为他消灭瘟疫和流行病的本事,逐步树立了崇高的声望。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回到科斯岛,在该地他创立并主管了一所医学院和一个医疗中心。他教导所有希望学习的人——只要他们付学费。他的医疗中心在希腊全境出了名,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病人和医生们。
当希波克拉底于一百零四岁(这完全是根据传说)去世时,科斯岛到处都是行医的人,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是他的门徒。争夺病人的竞争是激烈的,因而毫不奇怪,必须采取一致的行动来解决有关竞争的问题——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使医生的行为“合理化”,以便消灭“不公平的竞争”。
所以,在希波克拉底去世大约二十年以后(这也是根据传说),医生们聚集到一起创立了行为守则。他们以自己老师的名字给守则命名为希波克拉底誓约。此后,在科斯岛上并日益遍及世界其他地方,每一个新培训的医生,在他开业之前,都要宣誓忠于上述誓约。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美国已成为大部分医学院校毕业典礼的一部分。
象大多数职业法规、商业交易协定和工会合同一样,希波克拉底誓约充满了帮助病人的美好理想:“我将用自己的力量,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和判断力解除病人的痛苦。……无论来到哪一家,我都要帮助病人解除痛苦,而决不存心做损害或伤害人的事情。……”等等。
但是,该誓约也包含着一些同上述精神不相符的内容。例如誓约上有这样的话:“我将把医术、讲稿和所有其它学问传授给我的儿子、我师傅的儿子以及受过正式训练并宣过誓的人,而不传给别人。”今天,我们也许会把这称作封闭式雇用制度(即只雇用某一工会会员的制度)的前身。
誓约还提到了患有肾结石或膀胱结石的病人,原话是这样的:“哪怕是结石病,我也决不动手术,我将交给具有这种技能的医生来处理此事。”这可以说是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划分市场的极好协议。
我们猜想,当医学院的毕业班宣誓时,希波克拉底在九泉之下定然不得安宁。当年,他曾经把知识传授给每一个对医学感兴趣并且愿意交付学费的人。他可能会强烈反对那种划分市场的做法。自从制定出希波克拉底誓约到今天,全世界的医生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竞争的危害,一直采用了这种做法。
美国医学协会很少被看作是工会,人们认为它的作用远远超出了普通工会的范围。它向其会员及整个医学界都提供重要的服务。然而,它实际上是工会,而且我们认为,是我国最成功的工会之一。几十年来,它缩减了医生人数,抬高了医疗费用,同时阻止了来自外行业的人同“受过正式训练并宣过誓的”医生们相竞争——自然,这一切在名义上都是为了帮助病人。关于这一点,本书无须重复的是,医学界领导人确实真诚地相信,限制从医人数对病人有好处。现在,我们大家已逐步熟悉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为自己谋福利就是为社会谋福利。
随着政府在医疗事业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且承担越来越多的医疗费用,美国医学协会的势力日趋衰落。另一垄断集团即政府官僚集团正在取代它。我们认为,这种结果部分地是由该协会本身采取的行动造成的。
医疗事业方面的这种发展趋势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未来将得到什么样的医疗以及为此将付出多少费用可能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本章讨论的是工人。不是医疗事业,因此我们只讨论与工会有关的医疗事业方面的一些经济问题,从而说明运用于所有工会活动的原理。我们将把医疗事业目前遇到的其他一些重要而使人迷惑不解的各种问题暂且放在一边。
谁得到了好处?
医生在美国属于享有最高报酬的劳动者。这种状况对于已经从工会得到好处的人们说来并不是例外情况。尽管人们经常得到的印象是,工会保护低工资工人免受雇主的剥削,但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最成功的工会总是这样一些工会,其会员从事的职业需要熟练的技能,不论有没有工会,他们的工资都比较高。这类工会只是使本来已经很高的工资更高。
例如在美国,航空公司驾驶员每周工作三天,1976年他们的平均年薪是五万美元,而且这以后又有相当大的提高。在一份题为“航空公司驾驶员”的研究报告中,乔治·霍普金斯写道:“今天飞机驾驶员惊人的高薪金,与其说来自他们承担的责任或他们掌握的技术,不如说来自他们通过工会获得的受到保护的地位。”
在美国,最老的传统工会是行业工会,如木匠、水管工、泥水匠等工人组织的工会,他们同医生一样,也是技术熟练、工资较高的工人。最近,发展最快的工会——而且的确几乎是唯一有所发展的工会——是政府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中小学教师、警察、卫生工作者以及其他各种政府雇员)组织的工会。纽约市的市政工人工会,通过把该城市推到破产的边缘显示了它们的力量。
中小学教师和市政雇员的情况,说明了一条在英国已经清楚地得到了证明的一般原理。他们的工会不直接同支付他们会员薪金的纳税人打交道,而同政府官员打交道。纳税人和工会与之打交道的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愈松弛,政府官员和工会相互勾结牺牲纳税人利益的趋势就愈益加强——这是某些人把另一些人的钱用之于第三者身上的另一个例子。这就是为什么纽约等大城市中的市政工人工会比小城市中的市政工人工会强大的原因,同时也是随着政府对学校活动和教育经费的控制日益集中化,日益脱离地方政府,中小学教师的工会越来越强大的原因。
同美国相比,英国政府对更多的工业部门实行了国有化,其中包括煤炭工业、公用事业、电话和医院。在英国的国有化工业部门中,工会一般特别强大,劳资问题也最为严重。同样的因果关系也反映在美国邮政工人工会的力量中。
假定强大的工会的会员工资比较高,明显的问题就是:是因为工会强大,会员们才得到高工资呢;还是因为会员的工资高,工会才强大?为工会辩护的人宣称,会员的高工资可以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而且,一当全体工人都是工会会员时,所有工人都将领取高工资。
然而情况是复杂得多的。极为熟练的工人的工会无疑地能提高其会员的工资;可是,不论怎样都会得到高报酬的人,在组织强有力的工会方面是处于有利地位的。而且,工会提高某些工人工资的能力,并不意味着普遍实行工会制度会提高全体工人的工资。正好相反,这是产生误解的根本原因,强大的工会能为其会员赢得利益,首先是靠牺牲其他工人的利益。
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是了解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即需求法则:某种东西的价格愈高,愿意购买它的人就愈少。使某种劳动较为昂贵,这种劳动提供的工作机会就会减少。使木匠活较为昂贵,则建造的房屋减少,并且所造的这些房屋会采用木匠活不多的建筑材料和方法。提高航空公司驾驶员的工资,乘飞机旅行将变得更贵。乘飞机的人将会减少,因此对于航空公司驾驶员来说就业机会也会少一些。反过来说,减少木匠、飞机驾驶员的人数,他们就会得到较高的工资。缩减医生的人数,他们就能收取较高的酬金。
一个成功的工会可以减少它所控制的工作机会。其结果是,希望按照工会的工资标准获得这类工作的某些人,就不会达到目的了。他们被迫转向别处。更多的工人会寻找其他工作,压低了这些工作的工资。普遍组织工会不会改变这种局面。这对于找到职业的人意味着高工资,与此同时,对于其他人则意味着更多的失业。更为可能的是,会出现一些强大的工会和弱小的工会,强大工会的会员会象现在这样,在损害弱小工会会员利益的情况下得到较高工资。
工会领导人经常说可以通过减少利润来提高工资。这是不可能的:根本没有富余的利润来提高工资。美国的全部国民收入目前约有80%用于支付工资、薪金和小额优惠。余额的一半以上用于支付租金和贷款的利息。公司利润——这是工会领导人常常提到的——总额不到国民收入的10%。这还是纳税前的利润。纳税以后,公司利润大约是国民收入的6%。即使全部利润都投放进去,也几乎不可能使所有人都领高工资。而且,这不啻于杀鸡取蛋。最低限度的利润,为投资于工厂和机器以及发展新的产品和新的方法,提供了刺激。这种投资和这些革新,近几年来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率,并为高而又高的工资准备了必要的资力。
提高某些工人的工资必然损害其他工人。将近三十年以前,我们当中有人曾经估计,在我国平均约有10-15%的工人,通过工会或者类似美国医学协会这样的组织,得以使他们的工资比在没有工会的情况下多提高了10-15%,而另外85—90%的工人挣得的工资则因此而减少了大约4%。最近的研究表明,现在的情况大体上仍然是这样。高工资的工人工资越来越高,低工资的工人工资越来越低。
我们所有的人,包括由工会高度组织起来的人们,作为消费者,由于工会会员的高工资对消费品价格的影响而间接地受到损害。对于包括木匠在内的每一个人说来,房屋的售价太高了。工会阻挠工人运用他们的技能生产价值最高的东西,工人被迫从事那些生产率较低的活路。对于我们全体说来,可得到的物品的总量,比应有的数量要少。
工会力量的来源
工会为什么能够提高其会员的工资?工会力量的基本来源是什么?回答是:工会可以缩减可得到的就业机会,换言之,可以缩减适于从事某类工作的人数。通常在政府协助下,用实行高工资率的办法,工会得以缩减就业机会。同样在政府协助下,主要是通过发给许可证的方式,工会得以缩减合用者的人数。工会偶尔还同雇主相勾结,对其会员所生产的产品实行垄断,以这种办法来增加其力量。
实行高工资率。如果工会可以设法使承包人支付给水管工或木匠的工资不少于,比如说每小时十五美元。那将会减少这方面的就业机会。当然,这也将增加愿意从事这类工作的人数。
假定目前可以实行这种高工资率。那么,必须采取某种办法来在寻求这种有利可图的工作的人们中间分配有限的就业机会。已采用过的许多方法包括:搞裙带关系,即把工作保留给家庭成员;按照资历和学历招工;超额雇用工作所需要的人员,即随便安排工作;以及不折不扣的行贿受贿。由于牵扯到很多利害关系,因而采用哪种方法对于工会来说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某些工会不允许在公开会议上讨论有关资历方面的规定,因为这种讨论常常引起殴斗。为了优先获得工作而向工会官员们付酬金,是一种普通的行贿形式。工会采取的种族歧视措施虽然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但仍然是分配工作的另一种方法。如果申请工作的人过多,供分配的工作有限,则招工方法必定是武断的。用偏见及类似的不合理的方法来解决把谁关在门外的问题,这种做法常常得到“已入会者”的大力支持。种族和宗教歧视也渗入到了医学院校的入学方面,原因同上面一样,即可接受的申请者过多,因而需要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
让我们再来看工资率,工会采用什么方法实行高工资率呢?一种方法是采取暴力行动或以暴力相威胁:宣称如果雇主雇用非工会会员,或付给工会会员的工资低于工会指定的工资率,将毁坏雇主的财产或者殴打他们;宣称如果工人同意为较低的工资干活,就揍他们或破坏他们的财产。这就是工会在进行工资调解和谈判时,为什么经常伴随有暴力行为的原因。
一种更为容易的方法是取得政府的帮助。正因为这个缘故,工会都把总部设在华盛顿美国国会的附近,而且在政治活动上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霍普金斯在有关航空公司驾驶员工会的研究报告中特别提出:“该工会得到了联邦立法的充分保护,使职业航空公司驾驶员实际上成了受国家保护的人。”
政府帮助建筑工人工会的主要形式是戴维斯-培根法案,该联邦法令规定,凡是同联邦政府签订有价值二千美元以上合同的承包人,支付的工资率不得低于有关地区由劳工部长决定的“同等工人和技工普遍享有的”工资率。实际上,“在决定工资的绝大多数场合……不论建筑面积和种类如何,普遍享有的工资率”往往被规定为工会的工资率。后来,这一有关工资率的条款写进了其他许多有关联邦政府援建项目的法令,写进了三十五个州(截至1971年)颁布的有关建筑开支的法令,从而扩大了上述法案涉及的范围。实施这些法令的结果是,政府对于大量建筑活动实行了工会的工资率。
甚至使用暴力暗中也包含有政府的支持。一般说来,在劳资争议中公众是同情工会的,这导致了政府当局容忍在其他情况下决不会容忍的行为。在劳资争议中,某人的小汽车被推翻,工厂、商店或住家的窗子被捣毁,甚或有人遭到殴打并严重受伤,肇事者不大可能被罚款,更不用说去坐牢了,但如果在其他情况下发生同样的事情,情形就不一样了。
政府实行工资率的另一套措施是最低工资法令。颁布这些法令据说是为了帮助低收入者。其实,它们损害了低收入者。要求颁布最低工资法令的压力,来自那些在国会面前作证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人。这些人不是贫苦人民的代表。他们主要是劳联-产联以及其他劳工组织的代表。在这些工会中,没有一个会员挣得的工资接近法定的最低工资。尽管有一套关于帮助穷人的漂亮话,但他们主张提高最低工资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其工会的会员免受竞争的危害。
最低工资法令要求雇主们歧视技术低的人。没有人这么明说过,但事实确实是如此。且以受教育很少而没有什么技能的青少年为例,其劳务比如说每小时仅值二美元。他或她也许渴望为这种工资干活,为的是掌握较多技能,从而得到较好的工作。但最低工资法令宣称,只有雇主愿意付给他或她(在1979年)每小时二点九美元,这样的人才能受雇。也就是说,除非雇主愿意仁慈地把九十美分加到青少年劳务所值的二美元上面,否则他们是不会被雇用的。青年人因不能得到每小时二点九美元而失业,反而说这种境况比接受每小时二美元的工资而就业要强些,这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青少年特别是黑人青少年的很高的失业率,既是一种耻辱,又是社会动乱的一个严重根源。青少年失业率的增加主要是最低工资法令造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低工资是每小时四十美分。战时的通货膨胀曾使这个数目低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可言。此后最低工资急剧上升,1950年升至七十五美分,1956年上升到一美元。五十年代初期,全体工人的失业率大约为4%,青少年的失业率平均为10%——对于刚加入劳动大军的人们说来,10%的失业率也许比人们预料的稍微高了一些。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大致相等。在最低工资率急剧提高之后,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扶摇直上。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在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之间出现了差距。目前,白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在15-20%之间,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在35-45%之间。我们认为,在所有法令中,最低工资率法令是最歧视黑人的一项法令。政府先是开办中小学,其中许多青年人,特别是黑人青年,所受的教育很差,以致他们未能掌握必要的技能从事工资较高的工作。随后政府再一次惩罚了他们,阻止他们为了得到在职训练而为低工资干活。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帮助穷人的名义下进行的。
限制人数。实行工资率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限制可能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数。当雇主众多,难于实行某种工资率时,这种方法是特别有吸引力的。医疗事业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某工会的大量活动是以限制开业医生为目的的。
正象实行工资率一样,要想在限制人数方面获得成功,通常需要政府的帮助。在医疗事业中,发放医生开业许可证是关键问题:凡想要“行医”的人必须得到政府的许可。不用说,只有医生有可能被认为有能力判断医生候选人的资格,因此各州(在美国,发放许可证的工作在州政府的管辖权限之内,联邦政府不管此事)签发执照的部门通常由清一色的医生组成,或者医生占优势,这些医生一般又是美国医学协会的会员。
上述主管部门或州的立法机关提出了批准许可证的各项具体条件,实际上是让美国医学协会来左右获准开业的人数。条件包括:必须受过长期的训练,必须毕业于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并在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医院担任过实习医生。绝非偶然,“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和医院的名单,一般是与美国医学协会的医学教育和医院委员会公布的名单完全相同的。任何学校如不得到美国医学协会的医学教育委员会的批准,是建立不起来的,或即使建立起来,也不能维持很久。得到批准有时需要按照该委员会的意见限制医生人数。
在经济压力特别大的三十年代萧条时期,有组织的医学界显示了限制从医人数的巨大力量。尽管当时从德国和奥地利(那时都是先进医学的中心)涌入了大批受过严格训练的难民。但希特勒上台后的五年中,获准在美国开业的外国医生,并不比前五年多。
营业执照的发给被广泛用来限制各种职业的从业人数,特别是医学等职业的从业人数,在这类职业中有许多单个的开业医生,他们同大量的个别主顾打交道。象在医学中一样,主管发放执照的部门,主要是由该行业持有营业执照的成员组成——不论他们是牙医、律师、整容专家、航空公司驾驶员、水管工,还是殡仪业者。没有哪个职业如此冷僻,以致无须用发给执照的办法来限制从业人数。据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说:“在某州议会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各职业集团纷纷要求发给执照,其中有拍卖人、采矿者、房屋改建承包商、宠物饲养人、电学家、性病医生和性生活顾问、数据处理者、估价人以及电视机修理人。夏威夷州签发文身艺术家执照。新罕布什尔州签发避雷针推销员执照。”签发各种执照的理由总是一样的:保护消费者。然而,要发现真正的理由,我们得看一看在各州议会里是谁在为实行或巩固营业执照制度进行游说。游说者一律是有关从业人员的代表,而不是顾主的代表。千真万确,水管工也许比其他任何人更清楚地知道如何保护他们的顾客。然而,当水管工在背后竭力谋取合法权力以决定谁可以当水管工时,就难以把他们对顾客的利他主义的关心看成是主要动机了。
加强对本行业就业人数的限制,同时增加领有执照的开业者的业务,各有组织的职业集团总是千方百计使其业务活动范围规定得尽量宽一些。
通过签发执照限制从事各种职业的人数,其结果之一是创造出了一些新学科:例如在医学中出现了整骨术及脊柱按摩疗法,这些医疗科目试图采取发给执照的办法,限制其人数。美国医学协会已提出许多诉讼,指控一些脊柱按摩医生及整骨医生非法开展其他医疗业务活动,企图把他们限制在尽可能狭小的营业范围之内。而脊柱按摩医生和整骨医生则控告其他医生没有得到执照就实施脊柱按摩疗法和整骨术。部分地由于新的高度精密的手提设备的出现,最近在各类居民区中发展起一种新的保健服务项目,即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提供急救服务。这类服务有时由市政府或市政府的一个机构提供,有时由不折不扣的私人企业提供,这类机构的人员主要是医务辅助人员,而不是持有执照的医生。
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一个附属于城市消防队的上述私人企业的老板乔·多尔芬,描述该企业的效能如下:
在我们服务的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地区,这是一个拥有五十八万人口的县,在提供急救服务以前,因心脏病突然发作而心脏停止跳动的病人,通过住进医院而活过来并且病愈出院的不到1%。提供急救服务以后,仅在头六个月中,23%的心脏停止跳动的病人被成功地救活了,他们病愈出院并且回到了社会生产岗位上。
我们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实说明了一切。然而,说这同医学界有关系有时是很困难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更为一般地说,导致工人停工一个最经常的原因,是所谓管辖范围争议,即有关各职业业务活动范围的争议。曾采访过我们的一个广播电台记者,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他强调采访要短,以便在他的盒式录音机的录音带上只录一面。翻录音带的工作必须留给电工工会的一个会员去做。他说,如果他自己把它翻过来,当他回到广播电台时,录了音的磁带会被洗掉,采访就白费了。这种行为正同医生反对辅助医务人员提供急救服务一样,并且其动机也是一样的:增加对一个特殊集团的服务的需求。
工会和雇主的勾结。工会有时通过帮助工商企业联合起来规定价格或者分配市场来增强自身的力量,而规定价格或者分配市场等活动在反托拉斯法令条件下对工商企业说来是违法的。
从历史上说,三十年代的采煤业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事例。当时的两个格费伊煤炭法案试图为煤矿经营者共同规定价格的行为提供法律上的支持。当三十年代中期第一个法案被宣布为违反宪法的法案时,约翰·L.刘易斯以及他所领导的美国矿工联合会挺身担负起了重担。每当开采出来的煤炭量多到似乎将迫使价格下跌时,刘易斯就与采煤工业进行默契般的合作,通过号召罢工或停工,控制产量并从而控制价格。正如一个煤业公司的副董事长在1938年指出的:“他们(美国矿工联合会)已做了大量事情来稳定烟煤工业,并尽力使该工业能够继续盈利。虽然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但实际上他们按上述方式所作的努力……比起煤矿经营者自己的努力……要稍许更加有效一些。”
利益在经营者和矿工之间被瓜分了。矿工得到了高工资,这自然意味着更多的机械化和较少的矿工被雇用。刘易斯明确承认这种结果,并且更愿意接受这种结果——他把受雇的矿工的高工资看成是对受雇人数减少的一种充分补偿,假如受雇者都是该联合会会员的话。
矿工联合会之所以可以起这种作用,是因为工会不受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限制。利用这一便利条件从事非法活动的工会,与其说是工人组织,倒不如说是出售使整个行业卡特尔化的劳务的企业。卡车司机联合会也许是最受人注意的工会。关于詹姆斯·霍法以前的卡车司机联合会主席戴维·贝克(两人都已入狱),有一个或许不足凭信的故事。当贝克与华盛顿州的各啤酒厂就啤酒厂卡车司机的工资进行谈判时,他被告知他所要求的工资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东部啤酒”的价格会因此而低于华盛顿州的啤酒价格。他问东部的啤酒应该是什么价格,才能接受他要求的工资。有人回答说,东部啤酒每箱的价格应该是X美元。据说他当时许下愿:“从今后东部啤酒每箱的价格保准会变成X美元。”
工会可以而且的确经常为其会员提供有用的服务,例如:就会员的就业条件同雇主进行谈判,反映会员的疾苦,以及使会员感觉到有所依附,有所作为。作为自由的信仰者,我们赞成给予人们最充分的机会,自愿组织工会,并且认为工会可以提供会员所希望并愿意为此出钱的任何服务,只要工会尊重其他人的权利而且不使用暴力。
然而,工会以及职业协会等组织,并没有依靠严格自愿的活动和全体会员来达到其公开宣布的主要目标,即提高会员的工资。工会及类似的组织在使政府给予它们特权与豁免权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些特别权利使他们在牺牲其他工人和全体消费者利益的条件下,得以让它们的某些会员和官员受益。总的说来,受益者的收入要比受害者的收入高许多。
政府
除了保护工会会员之外,政府还通过了旨在一般地保护工人的大批法令:向工人提供补偿费的法令,禁止雇用童工的法令,规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法令,建立保证实行公平就业的各种委员会的法令,促进积极行为的法令,建立调节就业的联邦安全和卫生管理局的法令,以及其他不胜枚举的法令。
某些措施对工作条件的改善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大多数法令,如工人补偿费法令和童工法,在它们颁布以前,就已体现在人们的自觉行动中了,颁布这些法令也许只是对边远地区具有实际意义。其他法令,你知道后不要感到惊奇,既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害处。它们在减少普通工人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同时,却为某些工会和雇主提供了权力的来源,为官僚们提供了官职的来源。安全和卫生管理局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是一个可怕的官僚主义机构,人们已对它怨声载道。正如最近流传的一个笑话所说: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你知道需要多少美国人安一个电灯泡吗?另一个人回答说:需要五个人,一个人安灯泡,四个人填写环境影响报单以及安全和卫生管理局要求的各种报告书。
政府确实在很好地保护一类工人,即由政府雇用的工人。
马里兰州的蒙特戈梅里县,离美国首都华盛顿半小时的路程,是许多高级文职人员的住宅区。在美国所有的县份当中,该县是家庭平均收入最高的。蒙特戈梅里县每四个就业人员中,就有一个是为联邦政府工作的。他们不担心失业,有同生活费用指数相联系的薪金。退休后,他们享有文职人员养老金,这种养老金也同生活费用指数相联系,并且不依赖于社会保险。许多人又极力取得领取社会保险金的资格,成了所谓拿双份养老金的人。
上述高级文职人员在蒙特戈梅里县的许多邻人,或许是大多数邻人,作为国会议员、院外活动人员、同政府订有合同的公司的董事长,也与联邦政府有某种联系。同华盛顿周围的其他住宅区一样,蒙特戈梅里县的发展是迅速的。最近几十年中,政府已变成了一种十分可靠而且发展很快的行业。
所有文职人员,甚至低级文职人员,都受到了政府的良好保护。根据大多数的研究报告,他们的平均薪金要高于同等私人企业雇员的薪金,并且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他们享有大量的额外优惠,而且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职业安全感。
正如《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所说:当(文职人员)管理规章激增,录满二十一大本,堆起来高达大约五英尺的时候,政府主管人员感到越来越难于解雇雇员了。与此同时,提级和增加工资则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几乎没有刺激、不受任何人控制的官僚统治机构。……
去年符合增加工资条件的一百万人当中,只有六百人的工资没有增加。几乎没有一个人被解雇;去年丢掉工作的联邦工作人员不到1%。
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事例:1975年1月,环境保护局一名打字员上班一贯迟到,以致他的上司要求将他解雇。这件事办了十九个月。如果把记录有关步骤的纸张连在一起,足有二十一英尺长。为了满足所有规章制度方面的要求,满足所有劳资协议上的要求,缺少哪一步骤也不行。
卷入这一过程中的有这个雇员的顶头上司、局长和副局长、人事处长、局内该部门的主管人、两名雇员关系专家、专门的调研办公室以及该办公室主任。不用说,这一大串官员为此而做工作是用纳税人的钱来支付的。
在州和地方政府各级,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在许多州以及象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大城市中,情况或者同联邦政府相类似,或者比联邦政府还要糟糕。纽约市落到它目前实际上的破产状态,主要是由于市政雇员工资的急剧增长,也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对提早退休人员给与优厚的养老金。在拥有大城市的各州,政府雇员的代表常常是州立法机关中的主要特殊利益集团。
没人提供保护
以下两种工人是得不到任何人保护的:一种是仅有一个可能的雇主的工人,另一种是没有任何可能的雇主的工人。
那些实际上只有一个可能的雇主的人,往往可以得到很高的报酬,因为他们的技能实在罕见,价值极高,只有一个雇主能够加以充分利用。
我们三十年代学习经济学时,教科书中的标准例子是棒球大王巴比·鲁思。他作为棒球之王译名叫做“最佳击球手”,他是那个时代最最受人欢迎的棒球选手。当时有两个主要的棒球俱乐部,不论鲁思为它们中的哪一个打球,都能使运动场卖满座。纽约扬基俱乐部恰巧拥有最大的运动场,因而它可以比任何其他俱乐部付给鲁思更多的钱。结果,扬基俱乐部实际上成了他唯一可能的雇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巴比·鲁思不能获得高薪金,但确实意味着没有人保护他;他不得不同扬基俱乐部讲价钱,把不为他们打球作为他进行威胁的唯一武器来使用。
没有可能选择雇主的人大都是政府措施的受害者。其中一类人我们已经提到过,即那些由于法定最低工资而找不到工作的人。正象前面已经指出的,他们中间许多人是政府措施的双重受害者:低劣的教育加上高额最低工资,后者阻碍了他们获得在职训练。
依靠政府救济的人多少处于相似的境地。只有当他们能挣到的收入足以补偿救济金或其他政府补助的时候,就业才对他们有利。但他们的劳务也许对于任何雇主都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七十二岁以下的依赖社会保险津贴生活的人,情况也是这样。如果他们可以挣得超过某一限额的收入,他们就会失掉其社会保险津贴。这就是近几十年超过六十五岁而仍然工作的人所占的百分比,为什么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对男性来说,这一比重由1950年的45%下降为1977年的20%。
其他的雇主
许多雇主的存在,可以为大多数工人提供最可靠而且最有效的保护。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只有一个可能的雇主的人,几乎或者根本得不到保护。保护工人的是那些愿意雇用工人的雇主。雇主对工人劳务的需求,使得他们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向工人支付其工作的全部价值。如果某一雇主不愿交付,另一雇主会支付。真正保护工人的,正是这种争夺工人劳务的竞争。
当然,其他雇主的竞争有时激烈,有时不激烈。一些机会会相互冲突,而另一些机会却不被人们所知。雇主要找到理想的受雇者,受雇者要找到理想的雇主,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们的世界并非尽善尽美的世界,因而竞争不能提供十全十美的保护。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工人说来,竞争是迄今被人们所发现或发明的最好的,也即害处最少的保护。
竞争的这种作用是我们一再提到的自由市场的一种特性。其他雇主的存在保护了工人免受其雇主的剥削,因为他可以到别处干活。其他工人的存在保护了雇主免受工人的剥削,因为他可以雇用别人。其他卖主的存在保护了消费者免受某一卖主的剥削,因为消费者可以到别的商店买东西。
我们的邮政服务质量为什么低劣?我们的长途火车服务质量为什么低劣?我们的中小学教育质量为什么低劣?都是一个原因造成的,就是我们实际上只能从一处得到上述服务。
结论
当工会用限制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办法来为其会员获取较高工资时,这种较高工资是通 过损害其他工人的利益获得的,这些工人发现他们的就业机会减少了。当政府向其雇员支付较高工资时,这种较高工资是通过损害纳税人的利益获得的。但是,当工人们通过自由市场获得较高工资和较好工作条件时,当工人的工资由于各厂商为得到最好的工人彼此进行竞争,由于工人们为得到最好的工作彼此进行竞争而增加时,这种较高工资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这种较高工资只能来自较高的生产率、较大的资本投资以及更加广泛推广的技能。整个馅饼是增大了——不仅工人得到的份额增大,而且雇主、投资者、消费者乃至税收官员得到的份额也增大了。
这就是自由市场制度在全体人民中间分配经济进步的果实的方式。这就是过去两个世纪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得到巨大改善的秘密所在。
本节内容概述
当工会用限制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办法来为其会员获取较高工资时,这种较高工资是通过损害其他工人的利益获得的,这些工人发现他们的就业机会减少了。当政府向其雇员支付较高工资时,这种较高工资是通过损害纳税人的利益获得的。但是,当工人们通过自由市场获得较高工资和较好工作条件时,当工人的工资由于各厂商为得到最好的工人彼此进行竞争,由于工人们为得到最好的工作彼此进行竞争而增加时,这种较高工资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这种较高工资只能来自较高的生产率、较大的资本投资以及更加广泛推广的技能。整个馅饼是增大了——不仅工人得到的份额增大,而且雇主、投资者、消费者乃至税收官员得到的份额也增大了。
这就是自由市场制度在全体人民中间分配经济进步的果实的方式。这就是过去两个世纪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得到巨大改善的秘密所在。
附录失业的成因和种类
技术性失业
技术性失业,是由于科技进步而引发的失业潮,例如工业革命引发的大量劳动人口的失业:蒸汽机、织布机、电灯等的发明;以及近代的自动化机械手臂、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各式自动化剪票口、未来的自动驾驶汽车等等。技术性失业通常产生卢德派之类的反科技进步组织,不过他们的抗争没办法对技术进步造成实质的阻碍。
由于近代的工业革命(目前是互连网、物联网科技以及自动化机械)可能造成绝大数人都遭到技术性失业,所以不少社会学家在研究新的制度与对策,以应付大范围技术性失业而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例如无条件基本收入就是一例。
摩擦性失业
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是指当人们放弃原来的职业再寻找新的工作,可能需要花费一段时间而出现的失业状况。因就业市场的资讯不流通,可能使得一些企业未能在短期内找到适合的劳工,而劳工也未能在这段时间找到工作,于是造成短期的失业现象。
现代社会中还有另一种摩擦性失业问题,拥有高学历的人士不一定能找到符合自己喜好的工作,也不愿意投身低阶劳动市场工作,造成不屈不就的窘境。此类失业属于自愿型失业,并非被裁员造成的非自愿型失业。这种失业往往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如隐蔽青年、双失中年(失业和失婚)、增加政府开支等。
结构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是指市场竞争的结果或者是生产技术改变而造成的失业,通常由于就业市场并不平衡,某些行业正扩张,另一些则衰退,造成部分工人失业。结构性失业通常较摩擦性失业持久,因为失业人员需要再训练或是迁移才能找到工作。
结构性失业的出现是因为经济结构、体制、增长方式等的变动,改变了工作技能的要求,导致失业的发生。由于失业工人并不具有合适的技能,因此,若失业工人并没有接受再培训或进一步的教育,他们便不能再获聘任,结构性失业问题因而会持续,影响长远的经济发展。
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被归类为自然失业,经济学家视这两种失业为正常现象。劳动人口中,属于该两种失业的劳动人口数目占劳动人口总数的百分比等于自然失业率。
自然失业率:失业率(%)=(摩擦性失业 + 结构性失业)÷ 劳动人口×100%
长期失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长期失业的定义是持续失业达12个月以上的劳工,长期失业数据值得关注的价值在于;这种劳工几乎就等于结构性失业者,此类劳工长期连续在社会上没有收入,很大概率已经耗尽储蓄,等于注定失去房屋和食物的获取能力成为社会问题最大的来源和社会暴动因素,也无法自费学习新技能来脱贫,更难进入职场等于生活在一种恶性循环中。若长期失业者没有得到官方的外力帮助几乎无法摆脱现状,因此长期失业数据对于政府施政有参考意义。
周期性失业
周期性失业(cyclical unemployment)是指由于经济中的总需求减少,导致劳动人口过剩,从而出现失业情况。这种失业被归类为非自愿性失业,因为人们是有能力并且愿意工作,只是社会的总需求减少以致劳动人口的数目未能与经济体系内的部门所提供的职位数目配合。由于总需求减少,伴随着的是经济周期改变,经济步入衰退期一直到低谷。如何解决周期性失业向来是经济学家的重点研究对象,经济学界里提出数种方法,例如:工人或工会自愿降低工资;增加对企业部门的投资诱导,提高总需求;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补充私人投资的不足,填补和总需求的差距等等。[4]
季节性失业
还有一种季节性失业(seasonal unemployment),相对以上三种失业情况来说,季节性失业并不足以对所有行业产生影响,也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失业”的类别或原因之一。它的涵义是社会中存在一些行业会在某些节日之前或者过后发生的失业情况。它常见于某些低技术工业,例如企业或工厂为了在重大节日前(例如圣诞节)尽快完成一个指定数量的产品,于是雇用不少额外工人以求尽快完成客户的订单,但在节日后进行裁员行动,将那些临时性工人解雇以减低长期成本。
古典式失业
古典式失业(classical unemployment),它跟季节性失业一样,并不是真正失业的原因,它是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对失业情况的解释。1890年,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马歇尔发表的经济学原理内,提出了局部均衡理论。这种理论以供给和需求的市场均衡来解释市场上的交易,供给主要由生产成本组成,需求则是由人们对该商品的边际效用组成。如果在单个生产单位的角度来说,劳动的工资也与劳动的边际产品有关,后者是生产单位多雇用一个人时,那个新雇用工人可以生产的产品,这边际产品决定全体工人的工资。英国经济学家,也就是所谓的“古典学派”认为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它的价格就是实质工资(等于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然价格)也由市场的均衡状况决定的。倘若人为推高了工资(例如法律订下的最低工资),供给量大于需求量造成超额,或者工资高于工人的边际产量,于是工人将被解雇,部分工人顺理成章失业。这解释提供解决方法,就是解雇工人是市场调节供给量的手段。因为这可以:
令人为的工资变成均衡价格,该行业的就业市场回到局部均衡。
对生产单位来说,边际产量势必因可变生产要素的减少而增加,边际成本减少,生产单位能够维持利润最大化。
古典式失业受人为的工资率和边际产量影响,所以是自愿性失业。
需求不足型失业(Demand-Deficient Unemployment)
人们可能已经拥有工作,但他们的生产力未必得到充分的利用,于是便会形成需求不足型失业(demand-deficient unemployment)及/或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就业不足总是永远存在于任何制度的社会。因为部分人们可能不愿意每日长时间工作;或者经济根本没有足够的全职工作去吸纳这些闲置的劳动力;即使实施计划经济的社会,政府也可能为了实现充分就业,而令到每单位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减少。就业不足率不包含于失业率内:
就业不足率(%) =(就业不足的人口 / 劳动人口)× 100%
第9章 通货膨胀的对策
先让我们比较一下两张差不多大小的长方形纸片。一张的背面大部分是绿颜色,正面有一幅林肯像,在这纸片的每一个角上印有数目字“五”,还有些别的图案。你用这纸片可以换到一定数量的食物、衣服或其他货物。人们将愿意和你做这种交易。
另外一张纸片也许是从一本印刷精美的杂志上剪下来的,正面可能也印有一幅画像、一些数目字和其他图案。背面可能也是绿颜色的。可是它却只适于点火。
不同在哪里呢?五美元的钞票上面印的东西解答不了这个问题。上面只是简单地印着“联邦储备券/美利坚合众国/五美元”,还有些小字:“本券为合法货币,可偿付一切公债和私债”。不多年以前,在“美利坚合众国”和“五美元”之间还有“可兑现”字样。看来这能说明两张纸片之间的区别。但它只是意味着,如果你到联邦储备银行要求出纳员兑现,他将给你五张同样的纸片,只是那数目字“五”换成了“一”,林肯的像换成了华盛顿的像。如果你从换得的五张纸片中拿出一张进一步要出纳员兑换,他会给你一些硬币。如果你把这些硬币熔化掉(尽管这样做是非法的),当作金属出售,肯定卖不到一美元,现在票子上印的字样虽然同样不说明问题,但至少是比较老实的。合法货币的含义是,政府将接受它作为向它偿债和纳税之用,法院将承认它们可以清偿按美元计算的债务。为什么私人进行货物和劳务的交易时也应该接受它们呢?
简单些回答,这是因为接受它们的每一个人都相信别人也会接受。这些绿色纸片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它们有价值。大家都认为它们有价值,是因为经验告诉大家它们有价值。要是没有一种大家共同接受的交易媒介(或这种媒介的数量不够多),美国就只能运用它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的一小部分;然而,大家共同接受的交易媒介的存在,却依赖于某种约定俗成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接受了一种从某种观点看来不过是虚构的东西。
但不论是约定俗成还是虚构,都不是脆弱的东西。相反,拥有一种共同的货币是非常有用的,以至人们即使在信念受到极严重的挑战时也仍然死抱住这种虚构不放。我们将要看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货币发行者得以从通货膨胀中得到好处,从而诱使他们造成通货膨胀。但也不是说这种虚构是不可摧毁的:“不值一文”(not worth a Continental)这个短语,使人想起美国大陆会议为了支持美国革命而过量发行的大陆货币的虚构是怎样被摧毁的。
虽然货币的价值是虚构的,但货币却具有非常有用的经济职能。不过这也只是一层面纱。决定一个国家财富的“真正的”力量,是它的公民的能力、他们的勤劳和智慧、他们所能利用的资源以及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方式等等。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一百多年以前写道的,“简言之,在社会经济中,没有什么东西从本质上来说比货币更不足道的了;它仅仅是一种发明物,用来节省时间和劳动。它是一种机器,用来把事情办得便捷,没有它,同样能办事,只是不那么便捷罢了。而且它同其他许多机器一样,一旦出了毛病,就只发挥它特有的、独立的作用。”
这样描述货币的作用完全正确,只是我们得承认,社会拥有的发明物,哪一件出毛病时也没有货币造成的危害大。
我们已经讨论过一个例子:大萧条,那时由于急剧减少货币供应量,货币出了毛病。本章讨论的是相反的、更常发生的情况:由于急剧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出了毛病。
货币种种
历史上,曾有许多东西被当作货币。“金钱”(pecuniary)这个词,来自拉丁文中的“pecus”,意为“牛”。牛是许多曾充当货币的东西之一。其他还有盐、丝、毛皮、鱼干儿以至羽毛,在太平洋的雅浦岛上,人们曾用石头当货币。贝壳和珠子是用得最广的原始货币。在纸片和会计用的笔取得胜利以前,在比较先进的经济中,金属——金、银、铜、铁、锡——曾经是使用最广泛的货币。
所有这些曾用来充当货币的东西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在特定的地方和时间,人们接受它来交换货物和劳务,相信别人也同样会接受。
美洲早期的定居者用来同印第安人作交易的“瓦姆庞普”(wampum)就是一种贝壳,与非洲和亚洲使用的贝壳相类似。美洲殖民地使用过的一种最有意思、最富有启发意义的货币,是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使用的烟草货币:“1619年7月31日〔约翰·史密斯上尉登上美洲,在詹姆斯敦建立起在新世界的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之后十二年〕,弗吉尼亚州第一届议会通过的第一个法律就是关于烟草的,它规定‘上等烟草的价格为三先令一磅,次等烟草的价格为十八便士一磅。’……烟草成了当地的货币。”
烟叶在各个时期都被宣布为唯一合法的货币。直到美国革命以后很久,将近两个世纪的一段时期,烟草一直是弗吉尼亚州及其邻近殖民地的主要货币。殖民者就用它来购买食物、衣着,用它来纳税——甚至用它来买新娘子:“弗吉尼亚州的作家威姆斯牧师说,每当有船从伦敦到达的时候,去看看漂亮的弗吉尼亚小伙子们个个挟着一捆上好的烟草跑到岸边,每人带回一个美丽而贤惠的年轻妻子,是令人开心的事。”另一位作家引用了这段话之后说,“他们一定既漂亮又高大,才能挟着一捆一百到一百五十磅重的烟草飞跑。”
当时烟草和货币同时流通。它最初按英国货币规定的价格高于种植它的成本,于是种植者就一心一意的种,产量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应量不仅表面上有所增加,而且实际上确实增加了。与通常的情况一样,由于货币供应量比可以买到的货物和劳务的数量增加得快,因而发生了通货膨胀,按烟草计算的其他东西的价格急剧上涨。大约半个世纪之后这场通货膨胀结束时,按烟草计算的物价上涨了四十倍。
烟草种植者对这场通货膨胀极为不满。按烟草计算的其他东西的价格如果上涨,烟草能够购买的货物量就会减少。按货物计算的货币的价格,是按货币计算的货物价格的倒数。自然,烟草种植者要求政府提供帮助。于是通过了一项又一项法律,禁止某些人种植烟草;要求毁掉一部分已收获的烟草;禁止种植烟草一年。但这些都无济于事。最后,人们自己行动起来,结成一帮一伙,跑到乡下去毁坏地里的烟草:“破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议会在1684年4月通过了一项法律,宣布这些破坏分子的行动极其严重地扰乱了社会治安,他们的目的是颠覆政府。同时宣布,如果有八个以上的人纠合在一起毁坏烟草田,就要判他们叛国罪,处以死刑。”
烟草货币生动地说明了一条最古老的经济学法则,即格雷欣法则:“劣币逐良币。”烟草种植者在纳税或者支付其他按烟草计算的债务时,自然用质量最差的烟草,而保留质量最好的供出口,以换回“硬”货币,即英镑。结果作为货币而流通的往往是质量低劣的烟草。人们挖空心思把烟草弄得样子好一点:“马里兰州在1698年发现有必要通过法律来防止人们弄虚作假,人们经常在大桶的上面盖一层好烟叶,而下面塞的却是甘蔗叶。弗吉尼亚州在1705年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但显然并没有解决问题。”
“1727年烟票合法化后,”质量问题才有所缓和。“所谓烟票在性质上同存款单相类似,由验收人员签发。法律规定它可以在签发烟票的库房所在地区流通,并可以用它偿还一切债务。”尽管实行烟票制的弊病很多,“但直到十九世纪前夜,这种收据却起到了通货的职能。”
这并不是最后一次把烟草当作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和日本的集中营里,人们曾广泛地拿纸烟作为交易的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领军当局对德国的法定货币规定了远远低于收盘水平的最高限价。结果使德国的法定货币丧失了作用。人们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作交易,小交易用纸烟作媒介,大交易用法国白兰地酒作媒介——无疑,这两种东西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为流通的货币。路德维希·艾哈德的货币改革结束了这一富有启发意义的——而又具有破坏性的——插曲。
弗吉尼亚烟草货币所表明的一般原则,在当代仍然适用,虽然政府发行的纸币和叫做存款的簿记项目,取代商品和库房的进货收据,成了社会的主要货币。
现在仍然同当初一样,如果货币数量增加的速度,超过能够买到的货物和劳务数量增加的速度,就会发生通货膨胀,按这种货币计算的物价就会上涨。这同货币量为什么增加不相干。在弗吉尼亚州,烟草货币量增加,产生了按烟草计算的物价的上涨,是因为用劳动和其他资源生产烟草的成本急剧降低了。在中世纪的欧洲,金银是主要的货币,按金银计算的物价上涨,是因为西班牙从墨西哥和南美洲弄来的贵金属充斥欧洲市场。十九世纪中叶,世界范围按黄金计算的物价上涨,是因为人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后来,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1914年,物价上涨是因为成功地在商业上应用了氰化处理法,人们可以用这种方法从低品位矿石——主要是在南非——中提取黄金。
今天,大家接受的交易媒介,不同任何商品发生关系,在各大国,货币量由政府决定。政府,也只有政府,应对货币量的迅速增加负责。这个事实是造成人们目前对于通货膨胀的原因和治法众说纷坛的主要缘故。
造成通货膨胀的近因
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一种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疾病,如不及时制止会摧毁整个社会。
例子是很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和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有时一夜之间上涨一倍或一倍以上——在一个国家里为共产主义奠定了基础,在另一个国家里为纳粹主义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便利了毛泽东击败蒋介石。在巴西,通货膨胀率在1954年达到大约100%,由此产生了军人政府。比这严重得多的通货膨胀导致了1973年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倒台和1976年阿根廷庇隆政府的倒台,两国都由军政府接管了政权。
没有一个政府愿意承担制造通货膨胀的责任,哪怕是不那么恶性的通货膨胀。政府官员总是能够为通货膨胀找出种种理由——贪得无厌的企业家、得寸进尺的工会、挥霍浪费的消费者、阿拉伯的酋长、恶劣的气候、或者别的什么更不着边的理由。不错,企业家贪得无厌,工会得寸进尺,消费者挥霍浪费,阿拉伯酋长们提高了石油价格,气候经常不好。所有这些可以使个别商品的价格上涨;但它们不会造成物价的普遍上涨。它们可以造成通货膨胀率的一时涨落。但它们不会造成持续的通货膨胀,理由很简单:这些被指控的罪犯没有哪一个拥有印刷机,能印出那些装在我们口袋里的纸片,也没有哪一个可以合法地授权会计在帐册上记入与那些纸片相等的项目。
通货膨胀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现象。南斯拉夫,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其通货膨胀率在欧洲国家当中可以说属于最高之列;瑞士,一个资本主义的堡垒,其通货膨胀率则属于最低之列。通货膨胀也不是共产主义的现象。中国在毛泽东统治下几乎没有通货膨胀;意大利、英国、日本和美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十年里则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当今世界上,通货膨胀是印刷机带来的现象。
承认严重的通货膨胀无论在哪里都总是一种货币现象,这还只是理解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治法的开始。更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的政府过于急速地增加货币的数量,为什么它们明知有潜在的危害,还是要制造通货膨胀?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值得再稍稍谈一下上面那个命题,即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尽管这个命题意义非常重大,尽管大量历史事实证明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它却仍然广泛地遭到否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散布烟幕,试图掩盖它们制造通货膨胀的责任。
如果能买到的货物和劳务的数量——简言之就是产量——能够同货币的数量以同样快的速度增加,那么,物价会趋于稳定。物价甚至可能逐步下降,因为人们收入增多后,将希望以货币的形式保存更多的财产。通货膨胀发生在货币的数量明显地增加,而且增加速度超过产量的增加时,每一单位产量的货币量增加得越快,通货膨胀也越剧烈。在经济学里,也许没有哪个命题比这个命题更为正确的了。
产量受到可利用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限制,也受到知识水平和运用知识的能力的限制。产量至多只能相当缓慢地增加。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的产量每年平均增加约3%。即使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年代,每年产量的增长也只是在10%左右。商品货币的数量也受到同样的物质上的限制,不过正如烟草、新世界的贵金属和十九世纪的黄金等例子所表明的,商品货币的增长速度有时比一般产量的增长速度快得多。现代货币——即纸币和簿记项目——是不受物质限制的。货币数量,也就是美元、英镑、马克或其他货币单位的数量,可以以任何速度增长,而实际上它们的增长速度有时高得惊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流通货币平均每月增加300%以上,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多,物价也以同样的速度上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流通货币每月平均增加12,000%以上,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物价甚至涨得更多,每个月上涨近20,000%。
1969至1979年美国发生轻得多的通货膨胀时,货币的数量平均每年增加9%,物价每年上涨7%。这十年产量的平均增长率为2.8%,这一比率大体上是上面两个百分比之间的差额。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货币数量的增长一般远远超过产量的增长;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讲到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时,没有附加任何有关产量的条件。这些例子还告诉我们,货币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并不是完全相等的。但是,就我们所知,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例子:一场严重而持久的通货膨胀,不伴随着大致相等的货币增长速度;也没有这样的例子,货币数量的急速增加,不伴随着大致相等的通货膨胀率。
几张图表(图1-5)表明,近年来这种关系始终如此。图中的实线是有关国家每单位产量的货币数量,记录的是从1964年到1977年每年的情况。另一条线是消费品价格指数。为了便于比较,两条线都用平均值在整个时期中所占的百分比来表示(两条线都以1964-1977为100)。两条线必然具有相同的平均水平,但如果数字计算精确的话,两条线并不一定在任何一年都一样。
图1美国的两条线几乎重合在一起。正如另外几张图表所表明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美国所独有的。虽然别国两条线之间的距离比美国的要大,但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两条线都非常相象。不同的国家有很不相同的货币增长率。但无论是哪个国家,这种不同总有与之相称的不同的通货膨胀率。巴西是个最极端的例子(图5)。它的货币增长率高于任何其他国家,因而其通货膨胀率也高于其他国家。
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货币量的迅速增加是因为物价迅速增加,还是相反?一条线索是,在大部分图表上,表示某年货币量的点总要比那一年物价的相应指数早六个月。考察一下决定这些国家货币量的制度因素和大量历史事件,可以得到更为明确的证据。在这些事件中,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是十分清楚的。
一个极好的例子是南北战争。南方主要是靠印刷机来资助战争,在这一过程中,从1861年10月到1864年3月,通货膨胀率平均每月为10%。为了制止通货膨胀,联邦实施了货币改革:“1864年5月,货币改革生效,货币量减少了。一般物价指数显著下降……尽管当时联邦军队侵入,军事上濒于失败,对外贸易减少,政府陷于混乱,联邦军队的土气低落。减少货币量对物价产生的明显影响,超过了这些强大的力量。”
这些图表排除了许多被广泛接受的关于通货膨胀的解释。工会是方便的替罪羊。它们被指责运用垄断力量强求提高工资,这使成本增加,物价上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日本和巴西的图表所表现的关系同英国、德国以及美国的一样呢?在日本,工会的力量微不足道;在巴西,工会只有得到政府的默许才能存在,而且要受严密的控制;而在英国,工会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会都强大;在德国和美国,工会的力量也很强大。工会可以为其会员提供有用的服务,也可以通过限制别人的就业机会造成许多损害,但是它们不制造通货膨胀。工资的增加超过生产率的增加,这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
同样,企业家也不造成通货膨胀。他们提高标价,是其他力量的结果或反映。通货膨胀严重的国家的企业家,肯定不会比通货膨胀轻微的国家的企业家更为贪婪,一个时期的企业家也不会比另一个时期的企业家更为贪婪。那为什么通货膨胀在某些地方、某些时期比在别的地方、别的时期厉害得多呢?
另外一个常见的解释,特别是企图推卸责任的政府官员经常给予的解释,是说通货膨胀是从国外输入的。这个解释,当大国的通货通过金本位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是正确的。在那时,通货膨胀是一种国际现象,因为许多国家都用同一种商品作为货币,只要什么使得这种商品货币的数量较快地增加,就会影响到它们全体。但就近年来说,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它是正确的话,为什么不同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这样不同?七十年代初期,日本和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每年达30%以上,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10%左右,德国的不到5%。我们可以说通货膨胀是世界范围的现象,因为它同时发生在许多国家里——正如高额政府开支和巨额政府赤字是世界范围的现象一样。但通货膨胀并不是一种国际现象,因为每个国家能单独控制自己的通货膨胀……正如高额政府开支和巨额政府赤字不是由每个国家控制力以外的力量造成的一样。
关于通货膨胀的另一种常见的解释是生产率低下。但让我们来看一下巴西的情况。该国产量的增长率在世界上属于最高之列,而其通货膨胀率也属于最高之列。确实,影响通货膨胀的是每一单位产量的货币量,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实际上,产量的变化赶不上货币量的变化。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经济福利来说,没有什么比提高生产率更为重要的了。如果生产率每年增长3.5%,二十年后,产量就能增长一倍;如果每年增长5%,十四年后就可以增长一倍——差别甚大。但是,生产率对通货膨胀只起极微小的作用,货币才起主要作用。
阿拉伯酋长们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呢?它们给我们强加了沉重的负担。石油价格陡涨,减少了我们所能得到的货物和劳务,因为我们得出口更多的货物和劳务支付石油。产量的减少提高了价格水平。但那影响也就这一下子。价格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对通货膨胀率造成持久的影响。在1973年那次石油危机之后五年里,德国和日本的通货膨胀减慢了,德国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从大约7%减到不足5%,日本从30%以上减到5%。在美国通货膨胀在那次石油危机之后一年达到最高峰,约为12%,1976年降到5%,然后在1979年又升到13%以上。这些大不相同的经历,能用所有国家共同遭受的一次石油危机来解释吗?德国和日本是100%依靠进口石油的,可是它们在降低通货膨胀率方面,却比只有50%的石油依靠进口的美国、或是已经成为一个大石油生产国的英国做得好。
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基本命题上来。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货币量比产量增加得更快造成的。货币量的作用为主,产量的作用为辅。许多现象可以使通货膨胀率发生暂时的波动,但只有当它们影响到货币增长率时,才产生持久的影响。
货币为什么过度增加?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这个命题虽然重要,但它只是解答通货膨胀的原因和治法的开始。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指导我们找出根本的原因并限制可能的治法。但它只是解答的开始,因为更深一层的问题是货币为什么会过度增加。
不论烟草货币或是以金银为本位的货币是什么情况,就今天的纸币来说,货币的过度增加,从而通货膨胀,是政府制造的。
在美国,过去十五年左右货币加速增加,有以下三个相关的原因:第一,政府开支迅速增加;第二,政府的充分就业政策;第三,联邦储备系统执行的错误政策。
政府如果用征税或向公众借款的办法来增加开支,那将不会招致货币增长率加快,因而也就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支增多,而公众开支减少。政府开支的增加,被私人消费开支和投资开支的减少抵消了。但是,通过征税和向公众借款来增加政府开支,在政治上是不高明的做法。我们许多人欢迎政府增加开支,却很少有人欢迎增加捐税。政府向公众借款,会提高利率,从而减少私人对资金的利用,个人为购买新住宅获得抵押贷款以及企业借款都要付较高的利息,遇到较大的困难。
除此而外,政府增加开支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货币数量。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提到的,要做到这一点,美国政府可以让美国财政部——政府的一个部门——卖公债给联邦储备系统——政府的另一个部门。联邦储备系统用新印刷的联邦储备券或是为财政部记入一笔存款,来支付公债。财政部于是可以用这些现钱或是可以向联邦储备系统取现钱的支票来偿付账款。当这些新增的高功率的货币被它最初的接收者存入商业银行时,它就成了商业银行的储备,以此可以更大规模地增加货币量。
用增加货币量的办法资助政府开支,对于总统和国会议员都常常是最富有吸引力的。这使他们能够增加政府开支,给选民一些甜头,而无需征税来为此付出代价,也无需向公众借款。
美国近年来货币增加较快的第二个原因,是试图实现充分就业。这个目标,对于数目众多的政府计划来说,是值得称道的,但其结果却令人很不满意。“充分就业”这个概念的含义,比表面看来要复杂含糊得多。在一个生气勃勃的世界上,新产品层出不穷,旧产品不断被淘汰,需求从一种产品转向另一种产品,发明创造时常改变生产方法,总之,一切都在运动,因而,劳动力也应经常流动。人们从一种工作转做另一种工作,其间常空闲一段时间。有些人脱离他们所不喜欢的工作,却还没有找到另外的工作。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需要花费一段时间寻找工作,也需要一些时间体验各种不同的工作。此外,对劳动力市场的自由运行的阻碍——工会的限制、最低工资,等等——增加了工人找到合适工作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平均多少人就业算是充分就业呢?
在政府开支和政府税收方面,也有不对称的问题。凡认为有助于增加就业的措施,在政治上都是吸引人的。凡认为会增加失业的措施,在政治上都是不吸引人的。结果是造成政府政策上的一种偏向,政府总是试图实现不切实际的充分就业目标。
这与通货膨胀有双重关系。首先,人们认为政府开支有助于增加就业,政府税收会减少私人开支,从而增加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就业政策往往使政府增加开支、降低税收,用增加货币量的办法而不是用征税或向公众借款的办法来弥补由此产生的赤字。其次,联邦储备系统不用资助政府开支的办法也能增加货币量。它可以用新制造的高功率的货币买进已发行的政府公债,从而增加货币量。这使银行能够发放更大量的私人贷款,因而人们认为联邦储备系统买进政府公债有助于增加就业。在人们要求实现充分就业的压力下,联邦储备系统的政策同政府的财政政策一样具有造成通货膨胀的倾向。
这些政策并没有实现充分就业,而是带来了通货膨胀。正如詹姆斯·卡拉汉首相在1976年9月对英国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一篇有勇气的讲话中所说的:“我们过去常常认为,只要大手大脚地花钱就可以渡过衰退时期,可以用削减税收和增加政府开支的办法增加就业。现在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你们,这种抉择已不复存在;如果说它存在过而且起过作用,那也只是靠了给经济注射更大剂量的通货膨胀,而下一步接着就是更高水平的失业。这就是过去二十年的历史。”
美国近年来货币量大增的第三个原因,是联邦储备系统执行了的错误政策。联邦储备系统的政策在人们要求实现充分就业的压力下不但具有通货膨胀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由于该系统试图追求两个互不相容的目标而变得更为严重。联邦储备系统有权控制货币量,它在口头上赞成这个目标。但象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狄米特律斯(他躲开爱着他的海丽挪,而追求爱着另一个人的赫米亚)一样,联邦储备系统不是把心用在控制货币量上,而是用在控制它无权过问的利率上。结果在两条战线都遭到了失败:货币量和利率都大幅度波动。这种波动同样具有造成通货膨胀的倾向。联邦储备系统牢记1929年到1933年犯的灾难性的错误,在货币增长率向下波动时急忙加以纠正,而货币增长率向上波动时则反应非常迟钝。
政府开支增长、充分就业政策和联邦储备系统着迷于利率的后果,就象处在上坡道上的滑行车一样。通货膨胀率升升降降,每次上升都使通货膨胀达到一个较前次顶峰更高的水平,每一次下降都使通货膨胀保持高于前一次的低点。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政府税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增加,只是不象开支增加得那样快,在这种情况下,赤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增加。
这种情况并不是只发生在美国,也不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事。从远古以来,当权者——无论是国王、皇帝或议会——都想用增加货币量的办法来获取资源进行战争,建立不朽功业或达到其他目的。他们常常受到这种诱惑。每当他们真的这样做的时候,紧跟着就会发生通货膨胀。
近两千年以前,罗马皇帝戴奥克莱迁曾用“降低铸币成色’的办法使通货膨胀——用貌似银币的合金币代替银币,其中银的成分越来越少,不值钱的合金成分越来越多,直到只是“贱金属表面镀一层银子而已。”现代政府采用的方法是印纸币和入账——但那古老的方法并没有完全消失。一度曾经是足色的美国银币,现在变成了铜币,镀的一层甚至不是银而是镍。而且,一种小号的苏珊·B.安东尼铸币取代了一度是足色的银元。
政府从通货膨胀中得到的收入
用增加货币量的办法资助政府开支,看起来象在变魔术,能凭空变出东西来。举个简单的例子,政府建造一条道路,筑路费用新印的联邦储备券支付。看起来好象大家都得到了好处,筑路工人得到工资,可以用来买吃的、穿的、住的。没有谁缴更多的税。却在原来没有路的地方有了路。是谁付的钱呢?
回答是所有持有货币的人为这条路付了钱。新增加的货币因为被用来招收工人筑路而不是雇用工人从事其他生产性活动,因而物价上涨。新增加的货币进入流通过程,从筑路工人手里转到他们向之买货的卖主手里,从这些卖主又转给别的卖主,等等,从而物价的上涨得到了维持。物价上涨意味着,人们原先持有的钱现在只能买到比原先少的东西。为了在手头积存足够的钱,能够购买从前那样多的东西,他们将不得不节省开支,把一部分收入用来抵补这个差额。
增印纸币无异于对人们持有的货币征税。如果新增加的货币使物价上涨1%,那么,每一个持有货币的人实际上缴纳了一笔税款,数额相当于他持有的货币总数的1%。他现在必须持有额外的纸片(或存款)以得到同从前一样的购买力。这些额外的纸片同他口袋里或保险箱里(或入了账的)的其他纸片税款的收据。
同上述税款相对应的实物,是使用筑路所耗费的资源本来可以生产的货物和劳务。那些为维持原有货币的购买力而节省开支的人,放弃了这些货物和劳务,使政府能够把这些资源用于筑路。
由此,你可以理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讨论通货膨胀问题时,为什么会写出下面这样一段话:“摧毁现存社会基础的最狡猾而又最可靠的方法,莫过于发放通货。这一过程把经济规律的全部看不见的力量都投到破坏的方面,而这样做时使用的方法,一百万人中间也不会有一个人能够弄得清楚。”
新增印的货币和记入联邦储备银行账册的额外的存款,只相当于政府从通货膨胀中得到的收入的一部分。通货膨胀还自动提高实际税率,从而间接地增加政府收入。当人们的货币收入随着通货膨胀而增加时。收入便被推上较高的一档,税率也就提高。公司收入因为没有扣除足够的折旧费和其他成本也人为地膨胀。一般说来,如果通货膨胀率为10%而收入也增加10%的话,联邦的税收会增加15%以上——这样,纳税人要赶上趟就不得不越跑越快。这个过程使总统、国会、州长和议员们能够装作减税的样子,而他们真正做的不过是不让赋税一次增加得过多而已。每年都说要“减税”,然而从来没有减少过。相反,如果正确计算一下的话,赋税实际上增加了:在联邦政府一级,税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1964年的22%增加到1978年的25%;在州和地方政府一级,从1964年的10%增加到1978年的15%。
通货膨胀给政府带来收入的第三种方法,是为政府偿还——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叫做拒付——部分公债。政府借入的是美元,偿还的也是美元。但由于通货膨胀,它偿还的美元能买的东西要比它借入的美元能买的东西少。如果在这期间政府为债务支付的利息足以抵补债权人因通货膨胀受到的损失,那政府并不能因通货膨胀得到纯收益。但是就大部分公债来说,并非如此。储蓄券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假定你在1968年12月购进一张储蓄券,保留到1978年12月兑现。你在1968年花三十七点五美元购买为期十年的、面值为五十美元的储蓄券,到1978年兑现时你可得到六十四点七四美元(因为在这期间政府提高了利率以在某种程度上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但实际上到1978年,你要花七十美元才能买到1968年花三十七点五美元可以买到的东西。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不仅你取回的只有六十四点七四美元,而且你还得为你得到的和付出的之间二十七点二四美元的差额缴纳所得税。结果是你为有幸借钱给政府付出了代价。
靠通货膨胀来还债意味着,尽管政府年复一年有大量赤字,它的美元债务越来越多,但这债务就购买力来说远没有增加那么多,而且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还下降了。从1968年到1978年这十年间,联邦政府累计赤字超过二千六百亿美元,但负债额在1968年占国民收入的30%,1978年只占28%。
通货膨胀的医治
医治通货膨胀,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因为货币量的过度增加是通货膨胀的唯一重要原因,因而降低货币增长率是医治通货膨胀的唯一方法。问题不在于知道该做什么。这是很容易的。政府必须降低增加货币量的速度。问题是要有政治上的决心来采取必要的措施。通货膨胀这一疾病一旦到了晚期,医治它就得花很长时间,而且会有痛苦的副作用。
可以举两个医学上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例子是:一个青年得了布尔吉尔氏病,这种病将阻断血液供应,会导致坏疽。这个青年人将失去他的手指和脚趾。治法说来简单:就是戒烟。那青年人缺乏这样做的意志,他的烟瘾太大了。他的病在一种意义上是可以医治的,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无法医治。
另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酗酒。当酒鬼开始喝酒的时候,先是感到非常痛快,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则会感到头痛恶心,忍不住喝“解醉酒”来减轻痛苦。
通货膨胀的情况也是这样。当一个国家开始发生通货膨胀的时候,初始的效果似乎很好。增加的货币量使得任何因此而得到更多货币的人——当今主要是政府——可以多花一些钱,而无需任何别人少花钱。就业机会增多,生意兴隆,几乎可以说是皆大欢喜,这是最初的情况,也是好的效果。但随后,开支的增大使物价上涨;工人们发现他们的工资虽然按美元计算有所提高,可能够买到的东西却减少了;企业家发现他们的成本上升,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他们能够更快地提高价格,否则销售额的增加并不会带来他们所预期的利润。不良效果开始出现:物价上涨,需求缺乏弹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同时发生。和那个酒鬼一样,人们这时想的是更快地增加货币量,这就使我们坐上了前面提到的那种滑行车。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加大数量——酒或是货币——来给那酒鬼或是经济一个同样的“刺激”。
酗酒和通货膨胀相类似,医治的方法也相同。治酗酒的办法是干脆宣布:停止饮酒。这难以办到,因为这一回是不良效果在前,而好的效果在后。刚戒酒的人感到很难受,然后才能到达乐土,不再是几乎不可抗拒地想再喝一杯。通货膨胀也是这样。放慢货币增长率,在开始的时候会带来痛苦的副作用: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暂时偏高,通货膨胀率暂时并不降低多少。好处要在一两年后才出现:通货膨胀率降低,经济比较健康,有了非通货膨胀性迅速增长的潜势。
痛苦的副作用,是酒鬼或通货膨胀的国家难以戒除的一个原因。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至少在病的早期比第一个原因更为重要:即缺乏真正的戒除的愿望。饮酒者津津有味地品酒;不愿承认自己是酒鬼;也不认为应该去治疗。通货膨胀的国家处于同样的情况。它往往认为通货膨胀是暂时的现象,没有什么了不起,是异常的外部情况造成的,它会自行消失——可实际上通货膨胀从来没有自行消失过。
而且,我们许多人也喜爱通货膨胀。我们自然喜欢看到我们买的东西降价,或至少价格停止上涨。但是我们更喜欢看到我们卖的东西涨价——不论是我们生产的货物,我们的劳务,还是我们拥有的房屋或其他东西。农民抱怨通货膨胀,却聚集到华盛顿要求提高他们的产品的价格。我们其他人大都也这样或那样地做着同样的事情。
通货膨胀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原因之一,是别人吃苦头的时候有些人却得到很多好处;社会划分成胜者和败者。胜者认为他们碰到的好事,是他们自己的远见、谋虑和主动的自然结果。他们认为那些坏事,例如他们买的东西涨价,是他们所控制不了的外部力量造成的。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会说他反对通货膨胀;他的通常的意思是他反对他所碰到的坏事。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几乎每一个拥有房产的人在过去二十年间都因通货膨胀得到了好处,因为他的房子的价值急剧增高。如果房子是靠抵押贷款购买的,那利率通常低于通货膨胀率。结果,付了叫做“利息”和叫做“本金”的钱,就实际偿清了贷款。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定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是一年7%。如果你借入了一笔一万美元的抵押贷款,只付利息,那么一年之后,这笔贷款的购买力只相当于一年前的九千三百美元。实际上你就少欠了七百美元——正好是你付的利息的数目。实际算来,你使用这一万美元没有付任何东西。(由于在计算你的所得税时要除去这笔利息,你实际上还有所得。你借了钱还得到报酬。)对于房产拥有人来说,这种效果是明显的,因为他的房屋的价值迅速上涨。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为储蓄信贷协会、互济银行或其他机构提供资金,使它们能够发放抵押贷款的小储户来说,却是损失。这些小储户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政府严格限制这些机构付给其储户的最高利率——据说是为了保护储户。
因为高额政府开支是造成货币过度增长的一个原因,所以减少政府开支是有助于减少货币增长的一个因素。在这里,我们也倾向于患精神分裂症。我们都喜欢看到政府开支下降,只要不是对我们有利的开支;我们都喜欢看到赤字减少,只要是靠征别人的税来减少赤字。
但是,通货膨胀的加速发展,迟早会对社会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带来大量的不公平和苦痛,以至真正的公众意志会发展起来,对通货膨胀采取措施。通货膨胀发展到什么程度才会发生这种情况,要看有关的国家和它的历史。在德国,通货膨胀程度不高就会发生,因为德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过可怕的经验;在英国和日本,发生这种情形时的通货膨胀水平要高得多;而在美国还不曾发生。
医治的副作用
我们再三读到,较高的失业率和缓慢的增长是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我们必须面对的选择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或者较高的失业率;政府当局已安于或正在积极地促进较慢的增长和较高的失业率,以医治通货膨胀。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虽然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放慢了,平均失业水平也上升了,但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却越来越高。我们既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又有较高的失业率,二者兼而有之。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经验。这是怎么回事呢?
回答是,缓慢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失业率并不是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而是医治奏效时产生的副作用。许多政策在妨碍经济增长和增加失业的同时,又增加通货膨胀率。这就是我们采取的一些政策的情况——零星的物价和工资管制,政府对企业干预的增多,都伴随以政府愈来愈大的开支和货币量的急速增加。
另一个医学上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治法和副作用的区别。你患了急性阑尾炎,医生建议做阑尾手术,而且告诉你手术之后要卧床休息一段时间。你拒绝动手术,而是在床上躺那么一段时间,把这作为痛苦较少的治疗方法。人们也许感到这非常荒唐可笑,但这在各方面都同在失业问题上混淆副作用和治疗方法一样。
医治通货膨胀,副作用是痛苦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懂得为什么产生副作用,并设法减轻它们,产生副作用的根本原因,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说明了。那就是变化的货币增长率,对由物价制度传递的情报产生干扰,因而使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作出不适当的反应,而这需要时间来加以克服。
首先,考虑一下当货币开始膨胀性增长时会发生什么情况。用新创造的货币偿付的较高的开支,对于出售货物、劳动或其他劳务的人来说,同别的开支并无不同。例如,卖铅笔的人发现他能够按原先的价格售出更多的铅笔。他开始时就是这样做而没有改变铅笔的价格。他向批发商定购更多铅笔,批发商又向制造商订货,制造商又向原料供应商定货,等等。如果铅笔需求的增加是以其他某种东西的需求减少为代价,譬如说圆珠笔,而不是货币膨胀性增长的结果,则铅笔这方面订货的增加,会伴随着圆珠笔这方面订货的减少。铅笔,随后是用来制造铅笔的原料,会涨价;圆珠笔和制造圆珠笔的原料会跌价;但物价的平均水平并没有理由发生变化。
当对铅笔的需求增加是起因于新创造的货币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时,对铅笔、圆珠笔以及其他大部分东西的需求会同时增加。总的(货币)支出增多了。但是铅笔的销售者并不知道这一点。他还是象往常那样,开始的时候保持他平常的售价,愿意多卖一些铅笔,直到他认为他能够重新进货的时候。但是现在铅笔这个方面订货的增加,是同圆珠笔以及其他许多货物订货的增加一起发生的。由于订货的增加导致了对劳动和原料的需求相应增加,因而工人和原料生产者最初的反应会同零售商一样——加班加点增加生产,并且也提高价格,他们认为社会对他们提供的东西的需求增加了。但是这一次没有任何抵消物,没有大体上同增加的需求相当的减少的需求,没有同上涨的价格相当的下跌的价格。自然,这一点在开始时是不明显的。在一个富有活力的世界上,需求总是在变化,某些物价上涨,某些物价下跌。总的需求增加的信号往往同反映相对需求变化的特定信号混在一起。正因为这个原因,货币增长率加快的副作用看起来象是经济繁荣和就业人数增多。但迟早总的需求增加的信号会到达。
这一信号一旦到达,工人、制造商和零售商就会发现他们受骗了。他们对他们销售的那一点东西需求的增加作出反应时,误以为这需求增加是专对他们的,因此不会对他们购买的许多东西的价格产生很大影响。当他们发现自己错了时,他们就进一步提高工资和价格——不仅对需求的增加作出反应,而且把他们购买的东西的价格上涨也计算在内。我们于是就陷于物价和工资螺旋上升的过程中,这本身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货币的增加不进一步加速,对就业人数和产量的最初刺激就会转向反面;就业人数和产量都会因工资和物价的上涨而趋于下降。最初的一阵兴奋之后,就是醉醒后的不适。
发生这些反应需要时间。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在美国、英国和一些其他西方国家,大致平均要六到九个月,货币的增加才完成其经济过程,使经济和就业人数增长。再要十二到十八个月的时间,货币的增长才明显影响到物价水平,产生或加速通货膨胀。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所需要的时间之所以很长,是因为除战时外,这些国家的货币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的批发价格平均同二百年前差不多,美国的同一百年前差不多。在这些国家,通货膨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因而是一种新现象。通货膨胀率时高时低,没有一定的长期趋势。
许多南美洲国家没有那么幸运的遗产。在这些国家,货币增长对经济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要短得多——至多几个月。如果美国不纠正近来通货膨胀率大幅度变化的倾向,产生经济影响所需要的时间在美国也将会缩短。
放慢货币增长率后出现的情况,同上面说的情况一样,只是方向相反。开支的最初减少会被认为是对某些特定产品的需求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后,这将导致产量和就业人数的减少。再过一段时间,通货膨胀减缓,伴之以就业人数增加和产量提高。酒鬼经过一段最难熬的抑制时期,最后完全断了喝酒的欲念。
上述一切都是由货币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引起的。如果货币增长率高而且稳,物价逐年上涨,譬如说10%,则经济也许能够与此相适应。大家都会预计到这10%的通货膨胀率,因而工资每年会额外提高10%,同时利率也会额外提高10%——以补偿放债人因通货膨胀而遭受的损失;税率也将按通货膨胀率调整,如此等等。
这样的通货膨胀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也没有什么用处。它只是使事情不必要地复杂化。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局面不可能很稳定。如果制造10%的通货膨胀率在政治上是有利可图的,而且也是行得通的,那么,通货膨胀率一旦达到10%,人们就会得寸进尺,进一步提高通货膨胀率,使其达到11%、12%或15%。政治上可行的目标是不要通货膨胀,而不是使通货膨胀率达到10%。这就是经验的裁决。
缓和副作用
就我们所知,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例子:通货膨胀不经过一段经济增长放慢和失业率增高的时期而结束。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经验断定,没有办法避免医治通货膨胀的副作用。
但是,缓和这些副作用,使它们来得温和一些,是可能的。
缓和副作用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事先宣布一项政策并加以贯彻实施,使之取信于民,这样一来逐渐而平稳地降低通货膨胀率。
之所以要逐渐降低通货膨胀率并要事先予以宣布,是为了给人们时间作出调整——并劝诱他们这样做。许多人是根据他们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测订立长期合同的——合同的种类很多,有关于工作的,有关于借贷的,也有关于从事某项生产或建设的。这些长期合同使我们很难迅速减少通货膨胀,而且意味着,如果试图这样做的话,会使许多人遭受严重损失。但如果给予一定时间,这些合同就会满期,或予以修改,或重新谈判其条件,到那时合同就会适应新的情况。
另一种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缓和不良的副作用的方法,是在长期合同中加进所谓“调整条款”,即合同条件将根据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自动进行调整。最常见的例子是许多工资合同中载明的生活费用调整条款。这种合同规定,每小时的工资,将按通货膨胀率或通货膨胀率的一部分再加,譬如说2%的比率增加。如果采用这种方法,通货膨胀率低,按美元计的工资增加额也低;通货膨胀率高,按美元计的工资增加额也高;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工资的购买力都一样。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财产租赁合同的。租赁合同可以规定租金逐年按通货膨胀率调整,而不规定固定的租金。零售商店的租赁合同常常是规定租金按商店总收入的百分之几计算。这种合同表面上没有调整条款,但实际上却包含有这种条款,因为商店的收入会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增加。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贷款的。贷款一般是指按一定年利率供应的、在一定时期内必须偿还的、一定数目的资金,一笔一千美元的贷款,偿还期限可以规定为一年,年利率可以规定为10%。另外的做法是不把利率规定为10%,而是规定为譬如说2%再加通货膨胀率,这样,如果通货膨胀率是5%,利率就是7%,如果通货膨胀率是10%,利率就是12%。与此相类似的另一种方法是,不把偿还的钱数规定死,而是规定要按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就上面所举的简单的例子来说,借方所欠的数额是一千美元加上通货膨胀率再加上2%的利息。如果通货膨胀率是5%,他就欠一千零五十美元;如果通货膨胀率是10%,就欠一千一百美元;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要再加上2%的利息。
除了在工资合同方面外,调整条款在美国应用得并不普遍。但其应用范围正在扩大,特别表现在抵押贷款的可变动的利率上。另一方面,在差不多所有通货膨胀率很高而且变化很大的国家,这一条款则得到了广泛应用。
这种调整条款可以缩短放慢货币增长率后调整工资及物价所需要的时间,从而缩短过渡期,减少中间的副作用。然而,调整条款虽然有用,却远不是万应灵药。要让所有合同都这样调整是不可能的(例如纸币就不能这样调整),而且这样调整许多合同代价也很高昂。使用货币的最大好处正在于能够便宜而有效地进行交易,而普遍应用调整条款将减少这种好处。最好还是没有通货膨胀,因而不需要调整条款。这就是我们主张在私营经济中运用调整条款,只作为缓和因医治通货膨胀而产生的副作用的方法,而不作为永久性措施的原因。
在联邦政府部门里,调整条款则是很可取的永久性措施。社会保险、退休金、联邦雇员的工资(包括国会议员的薪金)以及其他许多政府开支项目,现在都按通货膨胀率自动调整。但有两个很显眼的不可原谅的缺口:所得税和公债。如果按通货膨胀率来调整个人所得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率,那么,物价上涨10%也将使税率提高10%,而不是象现在这样,税率平均提高15%以上。提高税率的情况将因此而不再出现,乱征捐税的现象也会从此而绝迹。这样做,还将减少政府对通货膨胀的兴趣,因为政府从通货膨胀中得到的收入将被减少。
公债利率也完全应该按照通货膨胀率调整。美国政府自己制造的通货膨胀,使得近年来购买长期公债成了非常不上算的投资。因而在政府发行长期公债的活动中应采用调整条款,以表明政府方面对公民的公正和诚实。
人们有时把工资和物价管制当作医治通货膨胀的一种方法。近来,由于工资和物价管制已显然不能医治通货膨胀,有人又极力主张用它来缓和医治通货膨胀的副作用。据称,工资和物价管制可以起这种作用,是因为这种管制可以使公众相信,政府是认真对付通货膨胀的。人们期望,这转过来会降低人们在订立长期合同时对未来的通货膨胀率的预计水平。
工资和物价管制如果用于这一目的,将阻碍生产的发展。它使价格结构歪扭,降低价格制度运行的效率。由此造成的产量下降加重医治通货膨胀的副作用,而不是减轻副作用。物价和工资管制浪费劳动,因为它一方面歪曲价格结构,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要花在建立、执行和逃避管制上面。不论管制是强制的还是标榜为“自愿的”,后果都是一样的。
实际上,物价和工资管制几乎总是用来代替货币和财政上的节制措施,而不是用来补充这种措施。这种经验使得参加市场活动的人把实施物价和工资管制当作一种表明通货膨胀在上升而不是下降的信号,因而导致他们预测的通货膨胀率偏高,而不是偏低。
物价和工资管制在实施后的一个短时期里常常看起来是有效的。表面上,牌价即计入物价指数的价格被压低,而暗地里人们则间接提高物价和工资——如降低产品质量,取消检修服务,给工人升级,等等。但当这些规避管制的简便办法用尽之后,价格结构便被扭得越来越厉害,于是被管制的压力达到沸点,不利影响愈来愈严重,最后整个计划归于垮台。其结果是加重通货膨胀,而不是减轻通货膨胀。回顾四千年来的历史,物价和工资管制的实施,没有哪一次不是由政治家和选民的目光短浅所造成。
实例研究
日本新近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医治通货膨胀的极好范例。由图6可以看到,在日本,货币量在1971年开始以愈来愈快的速度增加,到1973年中期,年增长率达到了25%以上。
直到大约两年之后,即1973年初,才发生相应的通货膨胀。其后,通货膨胀率的急剧增长使货币政策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重点从日元的国外价值——汇率——转到它的国内价值——通货膨胀。货币的增长被急剧削减,从年增长25%以上减到10%和15%之间。这样保持了五年之久,只有些小的例外。(由于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很高,所以货币增长率保持在这个幅度内可以使物价基本稳定。就美国来说,保持物价稳定的货币增长率是3-5%。)
在货币增长率开始下降之后约十八个月,通货膨胀率也跟着下降,但直到两年半后,通货膨胀率才降到两位数以下。随后,通货膨胀率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基本保持稳定——尽管货币增长率略有上升。然后,随着货币增长率的新的下降,通货膨胀率开始迅速地趋向于零。
图里面有关通货膨胀的数据是根据消费品价格计算的,批发价格的情况甚至更好些。批发价格在1977年中期以后实际上下降了。战后,日本工人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如汽车制造业和电子工业,这意味着劳务的价格比商品的价格涨得更快。因此,相对于批发价格来说,消费品价格有所上升。
日本在放慢货币增长率后,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特别是在1974年通货膨胀率还没有对放慢了的货币增长率作出明显反应之前。然后,生产开始恢复,接着增长——虽然增长率比六十年代的繁荣时期要低一些,但仍然相当可观:每年增长5%以上。在通货膨胀率下降的过程中,日本从未实行物价和工资管制。而通货膨胀率下降时,日本正在为适应石油价格上涨进行调整。
【译者按:西方经济学家为了各种不同的目的,经常用三种方式给货币供应量下定义,分别以M1、M2和M3来表示。就美国来讲,M1包括流通的纸币、硬币和商业银行中的活期存款;M2包括M1中的各项,再加上商业银行中的定期存款,但不包括巨额存款;M3包括M2中的各项,再加上非银行储蓄机构中的存款。】
结论
我们对通货膨胀的了解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五条:
1.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起因于货币量的急剧增加,而不是产量的急速增加(虽然货币增加的原因很多)。
2.在当今世界上,政府决定——或能够决定——货币的数量。
3.只有一种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即放慢货币增长率。
4.通货膨胀的发展需要时间——以年计算而不是以月计算;通货膨胀的医治也需要时 间。
5.医治通货膨胀的不良的副作用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在过去二十年间曾四次加速货币的增长。每一次货币量以更大幅度增长后,都是经济先得到扩充,随后便出现通货膨胀。每一次当局都用放慢货币增长率的方法制止通货膨胀。货币增长率下降后,紧接着就是一次通货膨胀性的衰退。再往后,通货膨胀率下降而经济情况好转。迄今,发展的顺序同日本从1971年到1975年的经验是一样的。不幸的是,关键性的差别在于我们没有表现出日本人那样的耐心,把节制货币增长的过程延续足够长的时间。相反,我们对衰退反应过分,加快货币的增长,开始又一轮通货膨胀,因而遭受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和更高的失业率的折磨。
我们被一种虚假的两分法引入歧途:要么是通货膨胀,要么是失业。这种选择法是虚幻的。真正的选择是:较高的失业率要么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的结果,要么是医治通货膨胀的一种副作用。
本节内容概述
1.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起因于货币量的急剧增加,而不是产量的急速增加(虽 然货币增加的原因很多)。
2.在当今世界上,政府决定——或能够决定——货币的数量。
3.只有一种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即放慢货币增长率。
4.通货膨胀的发展需要时间——以年计算而不是以月计算;通货膨胀的医治也需要时 间。
5.医治通货膨胀的不良的副作用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被一种虚假的两分法引入歧途:要么是通货膨胀,要么是失业。这种选择法是虚幻的。真正的选择是:较高的失业率要么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的结果,要么是医治通货膨胀的一种副作用。
流动性偏好,手中持有货币原因:交易动机、预防动机、投机动机
温和通货膨胀的好处:引导相对价格调整、促进资源有效配置、有助于实现充分就业
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鞋革磨损成本、菜单成本、扭曲相对价格造成资源错配、发出错误的价格信号干扰人们的判断、税收扭曲
未预期到的短期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收入、财富的再分配、有利于雇主、债务人、收入灵活者
通货膨胀分类: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动型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后果:收入增加、利率提高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后果:收入增加、利率下降
第10章 潮流在转变
由于西方各国政府未能达到它们所宣布的目标,所以人们普遍起来反抗大政府。在英国,这种反抗于1979年把玛格丽特·撒切尔推上了台,她在政纲中保证她的保守党政府将完全改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历届工党政府和前任保守党政府所遵循的社会主义政策。在瑞典,1976年这种反抗导致了社会民主党在连续执政四十多年之后的败北。在法国,这种反抗导致了政策的急剧转变,打算废除政府对物价和工资的管制,并大幅度减少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在美国,这种反抗最明显地表现在横扫全国的反纳税运动中,在这场运动中,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第13号建议”,其他许多州也通过了限制州政府税收的宪法修正案。
上述反抗也许将证明是短命的,过不了多久,也许政府就会重新获得更大规模的发展。目前人们只有减少政府税收和其他捐税的热情,而没有取消政府计划——除去有利于其他人的计划——的热情。反抗大政府的情绪,是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触发的,而各国政府是能够控制这种通货膨胀的,假如它们发现这样做在政治上是有利的话。如果它们控制住通货膨胀,反抗可能会减弱或者消失。
我们认为,与其说反抗大政府的情绪是暂时的通货膨胀引起的,倒不如说通货膨胀本身部分地是这种反抗情绪引起的。当用多征税的办法增加政府开支在政治上缺乏吸引力的时候,立法者就求助于通货膨胀来增加政府开支,通货膨胀是一种无须经过表决即可征收的隐蔽赋税,一种可以随意征收的赋税。这种方法在十八世纪不受欢迎,在二十世纪也同样不受欢迎。
另外,政府计划的表面目标及其实际结果之间,在各个方面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我们在前面各章一直在进行这种对比,以至连大政府的许多最强硬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政府的失败——可是他们的解决办法几乎总是更大规模地扩大政府的作用。
一种思潮一旦迅猛高涨,它就会排除一切障碍,排除一切对立的观点。同样,当它达到顶点时,一种相反的思潮则开始上升,而且也会迅猛高涨。
直到十九世纪后期为止,占统治地位的思潮是主张经济自由和限制政府的作用,亚当·斯密和托马斯·杰斐逊为宣传和推行这种主张做了大量工作。然后,思潮转变了——部分地是由于经济自由和限制政府的作用在导致经济增长及增进大多数人的福利方面的真正成就,这些成就使那些遗留下来的各种弊病(当然有许多弊病)变得越发突出,因而引起一种要消除它们的普遍愿望。于是倾向于费边社会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的思潮迅猛高涨,这种思潮改变了二十世纪早期英国政策的方向和大萧条以后美国政策的方向。
到目前为止,上述趋向在英国已持续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在美国持续了半个世纪。这种趋向也达到了顶点。由于期望总是落空,上述趋向的理性基础已遭到破坏。它的支持者正处于守势。除了更多的老办法外,这些支持者对于消除时弊已提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他们已唤不起年青人的热情,现在年青人感到亚当·斯密或卡尔·马克思的思想要比费边社会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远为激动人心。
尽管费边社会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的潮流已达到顶点,但至今仍无明确的证据证明代替以上潮流的,将是斯密与杰斐逊主张的更大自由和限制政府作用的潮流,还是马克思与毛泽东主张的万能的、铁板一块的政府的潮流。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无论是知识分子的舆论,还是实际政策都是如此。按照过去的经验来判断,先得有舆论,然后才能有政策。
知识界舆论的重要性
在第二章中讨论过的印度和日本的例子,证明了知识界舆论的重要性,这种舆论决定着大多数人及其领导人的轻率偏见,决定着他们对于一种行动路线或另外一种行动路线的条件反射。
1867年取得治理日本大权的明治时代的领导人,主要致力于加强其本国的威力和荣誉。他们认为个人自由和政治解放没有特别的价值。他们相信贵族政治和由优秀分子实行的政治统制。可是,他们采取了自由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对民众说来导致了机会的扩大,并且在最初几十年中,这种政策还导致了更大的人身解放。另一方面,在印度取得领导权的人们,热忱地献身于政治自由、人身解放和民主。他们的目的不仅是国家的威力,而且还有公众经济条件的改善。但是,他们采取了集体主义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束缚了印度人民的手脚,不断削弱曾受到英国鼓励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获得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解放。
政策上这种差异如实地反映了两个时代不同的知识界的思潮。十九世纪中叶,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新的经济应通过自由贸易和私人企业加以组织。日本领导人大概根本没有想到要遵循任何其他路线。二十世纪中叶,人们则理所当然地认为,现代经济应通过集中控制和一系列五年计划加以组织。印度领导人或许根本没有想到要遵循任何其他路线。这两种观点都来自英国,倒是一件有趣的轶闻。日本人采用了亚当·斯密的政策。印度人采用了哈罗德·拉斯基的政策。
我们自己的历史同样有力地证明了舆论的重要性。舆论影响了一群卓越的人的工作。他们于1787年聚集在费城的独立大厅内,为他们帮助创立的新国家起草了一部宪法。他们对历史了解很深,并深受英国思潮的影响——正是这一思潮后来影响了日本的政策。他们把权力的集中,特别是集中在政府手里,看成是对自由的巨大威胁。他们起草宪法时牢记了这一点。美国宪法力图限制政府权力,保持地方分权并赋予个人以支配他们自己生活的权利。同宪法原文相比,在人权法案和宪法的前十项修正案中,上述意图更为明显:“国会不得制定确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或者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之法律”;“不得侵害人民保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用宪法中列举的某些权利取消或轻视人民的其他权利”;“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或未禁止各种行使的权力,皆由各州或人民保留之。”(摘自第一项、第二项、第九项及第十项修正案)
十九世纪后期以及进入到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美国知识界的舆论——主要处于来自英国的观点的影响之下,这类观点后来影响了印度的政策——开始发生了变化。它从相信个人责任和依靠市场转到相信社会责任和依靠国家。到了二十年代,大多数(即使实际上不是大多数,也是强有力的少数)关心公众事务的大学教授都持有社会主义观点。《新共和》周刊和《民族》双周刊是当时最主要的表达知识界见解的两种杂志。由诺曼·托马斯领导的美国社会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其主要力量却在大专院校里。
我们认为,在二十世纪前几十年中,社会党是美国最有影响的政党。因为它没有希望在全国范围取得选举胜利(不过也确实有少数社会党人当选为地方官员,尤其是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市),它成了一个坚持原则的政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则不是这样。为了把根本互不相关的各种派别和各种利益集团结合到一起,民主党和共和党成了搞权宜之计和妥协的政党。它们不得不避免“极端主义”,保持中间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说它们是完全一样的两个政党——但实际上它们不同的地方确实很少。不过,最后这两个主要政党都采取了社会党的立场。社会党得到的总统选票从未超过6%(1912年尤金·德布斯所得)。它1928年得到的选票不到1%,1932年仅为2%(诺曼·托马斯所得)。可是,该党1928年总统竞选政纲里的几乎每项经济政策,现在都被法律固定了下来。
一旦知识界舆论的变化影响到更广大的公众,正象大萧条后发生的情况那样,在一种大不相同的舆论影响下制定的宪法,证明至多只能推迟政府权力的增长,而不能阻止政府权力的增长。
用社利先生的话来说,“不论是否符合宪法精神,最高法院都可以自由解释宪法。”宪法的词句被重新解释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那些旨在阻止政府扩张权力的词句遭到漠视。正如雷奥尔·伯杰在仔细考察最高法院对一项修正案的解释时写道的:
最高法院对第十四项修正案的解释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了最高法院如何“行使”哈兰法官所说的“修正权”,也就是在解释含义的名义下不断修改宪法的权力。……
可以有把握地说,最高法院无视宪法制订者的意愿,对宪法作了完全违反原意的转释。……
这样的行为使人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最高法院的法官就是法律。
思潮和人民的行为
费边社会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的思潮已达到顶点的证据,不仅来自知识分子的著作,来自政治家们在竞选讲坛上表明的观点,而且也来自人民行为的方式。他们的行为无疑受到思潮的影响。反过来,人民的行为也加强着这种思潮,并且在把这种思潮变成政策的过程中起着较重要的作用。
正如A.V.迪塞以卓越预见于六十多年以前写道的:“假如社会主义立法的进展受到抑制,这种挫折与其说归因于任何思想家的影响,不如说是归因于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某些明显事实,例如增税显然是社会主义政策通常的伴随物,假如不是永恒的伴随物的话。”通货膨胀、高额税率以及工作效率明显低下、官僚统治和来自大政府的过多管制,都在发挥迪塞所预期的作用。所有这一切迫使人民不得不自己管理自己,不得不想办法绕过政府设置的各种障碍。
帕特·布雷南在1978年成了有几分名气的人,因为她和她丈夫同美国邮政局展开了竞争。他们在纽约的罗彻斯特的一间地下室里开始了营业,保证把投寄罗彻斯特商业区的包裹和信件于他们收到的同一天送到指定地址,收费标准低于国家邮政局的标准。他们的营业很快兴旺起来。
毫无疑问,他们违犯了法律。邮政局到法院控告他们,这场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他们失败了。当地的企业家曾给予他们财政上的支持。
帕特·布雷南说:
我想人民将进行一种温和的反抗,或许我们就是这种反抗的开端。……你看到人民在反对官僚,若干年以前你不能想象会这样做,因为你会受到镇压。……人民决定:他们的命运是属于自己的,而不属于在华盛顿的毫不关心人民的人。因此,这不是搞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而是人民重新考虑官僚们的权力并且对它加以抵制的问题。……
在各行各业中,人们又提出了自由的问题——你是否有权利从事某种职业,以及是否有权利决定怎样从事这种职业。在消费者利用他们认为是廉价的和优良得多的服务方面,也有自由的问题,按照联邦政府的看法以及被称为私人快速邮递法令的法律正文,我没有自由开办一个企业,消费者也没有自由去利用它——在我们这样一个完全以自由和自由企业为基础的国家中会发生这种事情,怎么能不令人感到非常奇怪呢。
帕特·布雷南对其他人企图控制她的生活作出了人人皆有的正常反应,因为她认为她的生活与他们毫不相干。最初的反应是忿恨;随后便试图用合法的方式绕过各种障碍;最后是对法律的蔑视。这个最后的结果是可悲的,但却是不可避免的。
在英国,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人们对没收性赋税作出的反应。英国的一位权威人士格雷厄姆·特纳说道:
我认为,可以完全公平地说,在最近十或十五年的过程中,我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弄虚作假者的国家。
人们是怎样弄虚作假的呢?人们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做到这一点。让我们先从最低阶层谈起。且以乡下的一个小杂货商人为例。……他是怎样赚钱的?他发现通过正式的批发商进货,他得经常使用发票,可是如果他现购自运,……商品的利润额便可以逃税,因为税务稽查员根本不知道他已拥有这些商品。这就是他赚钱的办法。
现在让我们来看最高阶层的情况,例如公司董事,他们使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方法弄虚作假。他们通过公司购买食品,以出差的名义度假,安排自己的妻子当公司董事,即使她们从未到过工厂,他们利用公司的材料为自己盖住宅,方法简单得很,就是在公司建造厂房时动手盖住宅。
从下到上,从干着极卑微工作的劳动阶级一直到最上层——企业家、高级政治家、内阁成员、影子内阁成员——都在弄虚作假。
我认为几乎每个人现在都感到,税收制度非常不公平,而且每个有办法的人都试图找到一种方法躲过税收制度。因为现在人们一致认为税收制度不公平,所以国家事实上变得有点象阴谋集团——大家互相帮助去弄虚作假。
你在这个国家里弄虚作假是没有困难的,因为其他人实际上愿意帮助你。可在十五年以前情况是全然不同的。人们会说,嗨,怎么会出现这种完全不应该有的事呀。
《华尔街日报》(1979年2月1日,第18页)曾刊登过梅尔文·B.克劳斯撰写的一篇题为“瑞典人的抗税”的文章,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这篇文章中以下的内容:
针对西方最高的赋税开展的瑞典革命,是以个人的首创精神为基础的。瑞典老百姓不是依赖政治家,而是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干脆拒绝纳税。有几种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其中一些办法是合法的。……
瑞典人拒绝纳税的办法之一是少干活。……在斯德哥尔摩美丽的多岛屿的海上坐船游览的瑞典人,生动地说明了这个国家秘密的赋税革命。
瑞典人运用亲自动手的办法逃避纳税。……
物物交换是瑞典人逃避高额赋税的另一种办法。要诱使一个瑞典牙医离开网球场坐在他的诊所里给病人看病,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可是一个患牙疼的律师却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作为回报,律师可为牙医业务提供法律服务。进行物物交换使牙医节省了两笔税款:他本人的所得税和应为律师酬金缴纳的税。尽管物物交换本来是原始经济的标志,但瑞典的高额赋税却使得它在这个福利国家,特别是在各种专门职业中成了一种受人欢迎的交易方式。……
瑞典的赋税革命不是富人的革命。在各个收入阶层都在发生这种革命。
瑞典这个福利国家正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它的思想体系促使政府不断增加支出。……可是,对于瑞典公民来说,赋税负担则有其饱和点,一旦达到饱和点,他们就会起来反对进一步增税。……瑞典人抵制高额赋税的方法,有损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日益增长的政府支出是在挖福利经济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的墙脚。
为什么特殊利益占优势
如果费边社会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的潮流已达到顶点,继之而来的不是极权主义社会,而是较为自由的社会和权力较为有限的政府,那么,公众不仅必须承认当前状况的缺陷,而且必须认清这种状况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为什么政策的目标很好,而结果常常适得其反?采用什么方法能阻止这一进程,或者使它倒转过来?
集中在华盛顿的权力
每当我们来到我国首都华盛顿的时候,都对集中在这个城市里的巨大权力惊叹不已。漫步在国会大厦,我们很难看到那四百三十五名众议员和一百名参议员,因为这里有一万八千名政府雇员,平均每个参议员约有六十五名雇员,每个众议员约有二十七名雇员。另外,还有一万五千多名正式的院外活动集团成员,身后经常跟着秘书、打字员、调查研究人员或者他们所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在国会大厦里串来串去,伺机施加影响。
而这仅仅是冰山之巅。联邦政府雇用着近三百万文职人员(不包括穿军服的武装力量)。有三十五万人以上在华盛顿以及附近的郊区工作。还有无数人间接地被政府雇用,雇用他们的是同政府订有合同的名义上的私人机构。另有一些人被劳工组织或资方组织或其他特殊利益集团所雇用,这些组织或集团都在华盛顿设有自己的总部或者至少设有一个办事处,因为华盛顿是政府所在地。
对律师们说来华盛顿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全国许多最大的最富有的法律事务所都设在这里。据说在华盛顿仅在联邦机构或管制机构中工作的律师就有七千多名。一百六十多家其他地方的法律事务所在华盛顿设有办事处。
和苏联、赤色中国或邻近美国的古巴等集权主义国家的权力不同,在华盛顿的权力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铁板一块的权力。权力被分割为许许多多的小块。全国各地的每一个特殊利益集团都试图尽可能地把它们的手伸到力所能及的不管什么样的权力上面。其结果是,政府几乎在每个问题上都脚踏两只船。
例如,在华盛顿的一座大楼里,一些政府雇员正在整天工作,试图制订和执行各种计划,用我们的钱劝阻人们不要吸烟。而在另一座距离不太远的大楼里,另外一些同样具有献身精神并且同样努力工作的雇员,整天工作以便用我们的钱补助农场主们去种植烟草。
在一座大楼里,工资与物价稳定委员会正在加班加点工作,试图用软硬兼施、连蒙带吓的方法迫使企业家降低产品价格,并用同样方法迫使工人降低他们的工资要求。而在另一座大楼里,农业部的某些下属机构则正在执行各种计划,以维持或提高食糖、棉花以及其他许多农产品的价格。在另外一座大楼里,劳工部的官员们根据戴维斯-培根法案,正在确定所谓“普遍实行的工资”,以此提高建筑工人的工资率。
国会建立了一个雇用二万名职工的能源部,以促进能源的保护。国会还建立了一个雇用一万二千名以上职工的环境保护局,它颁布了各种规章制度和命令,其中大部分要求使用更多的能源。无疑,在每一个机构里面,又各有一些下属单位,它们的工作目的也是互相矛盾的。
如果造成的结果不是如此严重的话,所有这一切似乎是非常荒唐可笑的。虽然上述各种机构的许多作用可以相互抵消,但它们的花费并不能相互抵消。每一个计划都要从我们口袋里掏钱,这些钱我们本来可以用来购买满足我们各种需要的商品和劳务。每一个机构都使用着能干的、技术熟练的人员,这些人员本来可从事生产性活动。每一个机构都挖空心思制订出各种条例、规则、繁琐的办事程序和需要填写的表格,这一切都在折磨着我们大家。
集中起来的利益与分散的利益
权力的分散和各项政府政策的相互矛盾,其根源在于民主制度的政治现实,这一制度是通过制订详细而具体的法律而运转的。这样一种制度往往把过大的政治权力赋予利益高度集中的小集团;往往比较重视政府行动的明显的、直接的和即刻显示出来的效果,而不重视政府行动的可能更重要的但却是隐蔽的、间接的和迟缓的效果;往往为了特殊利益而牺牲普遍利益,而不是相反。在政治生活中似乎也有一只无形之手,其作用恰好与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之手的作用相反。本意想要普遍利益的人们,受这只无形的政治之手的指引,促进了并非他本意想要促进的特殊利益。
这个问题的性质只需举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让我们先来看政府帮助海运业的计划,该计划的内容包括向船舶建造和营运业务提供补贴,以及限定大部分沿海运输业务由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来经营。据估计纳税人每年为该计划支付的费用大约六亿美元——或者换句话说,纳税人每年要为积极从事这一行业的四万人当中的每个人花一万五千美元。船舶所有者、经营者以及他们的雇员,受到强烈刺激去获得并保持这个份额。他们毫不吝惜地出钱对议员进行游说以及捐助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六亿美元分摊到二亿多人口上,平均每人每年出三美元,一个四口之家每年出十二美元。我们当中有谁会投票反对一个国会议员候选人,只因为他把上述费用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当中到底有多少人认为值得花钱挫败上述措施,或者甚至认为值得花时间了解这类事情?
另一个例子是,各钢铁公司的股东们、这些公司的总经理们以及钢铁工人都很清楚地知道,钢铁进口量的增加,对他们说来将意味着收入下降和工作机会减少。他们很清楚,政府排斥进口的行动会给他们带来好处。而出口行业的工人则不知道他们的工作受到了威胁。他们将失掉工作,因为减少从日本的进口必然减少对日本的出口。当他们丢掉工作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会丢掉工作。汽车或厨房的火炉或其他钢铁制品的买主们,可能抱怨他们不得不付较高昂的价格。限制钢铁进口迫使工厂主采用高价的国产钢铁以代替低价的外国钢铁;但有多少买主会把价格的提高追溯到这种限制呢?他们责备的对象很可能是“贪得无厌的”工厂主或者“得寸进尺的”工会会员。
农业是另一个例子。农场主们为了获得提价的支持,开着拖拉机来到华盛顿游行示威。政府作用的变化使得他们出现在华盛顿成了自然的事情,在此以前,他们只会责怪恶劣的气候,到教堂祈祷,而不是去白宫寻求帮助。甚至对于象食品这样必需和明显的产品说来,在华盛顿也没有消费者游行以抗议支持提价。尽管农业是美国的主要出口行业,农场主们并没有认识到事情到了这一地步是政府干预对外贸易造成的。例如,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他们可能因限制钢铁进口而受到损害。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完全不同的即有关美国邮政局的例子。解除政府对第一类邮件(即不受检查、邮资最贵的密封邮件)垄断的每一个行动,都遭到了邮政工人工会的坚决反对。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对私人企业开放邮政业务可能意味着他们会丢掉工作。防止出现这种结局对他们是有利的。正如罗彻斯特的布雷南夫妇经营邮政业务的实例所表明的,如果废除政府对邮政事业的垄断,将会出现一个生气勃勃的私人邮政行业,该行业将由几千家企业所组成,雇用几万名工人。那些可能在这样一种行业里找到好工作的人,几乎没有一个知道废除国家垄断会使他们找到好工作。他们肯定不会去华盛顿向有关的国会委员会作证。
一个人从某一项与他有特殊利益的计划中获得的好处,可能不足以抵偿对他有轻微影响的许多计划使他付出的代价。可是,对他有利的却是支持某一项计划,而不是反对其他计划。他很容易看到,他和具有同样特殊利益的小集团,花得起足够的金钱和时间促使对他们有利的计划得以通过。不促进对他有利的计划,并不会阻止其他对他有害的计划被采用。要做到这一点,他得象主持自己的计划那样,竭尽全力反对其他每一项计划。这显然是一桩赔本的买卖。
公民们是注意赋税的——可是就连这种注意也因多数赋税的隐蔽性质而被分散了。公司税和货物税包括在人们购买的商品价格之内,而没有单独的账目。大部分所得税在发工资以前就被扣除了。通货膨胀是最为恶劣的隐蔽赋税,不容易被人理解。只有销售税、财产税和超过扣除额的所得税,能够直接被人痛苦地感觉到——人们所怨恨的正是这些赋税。
官僚机构
政府的单位越小以及分派给政府的职能所受到的限制越多,政府的活动不反映普遍利益而反映特殊利益的可能性就越少。新英格兰的市镇会议是我们所想到的典型。被治理的人民了解而且能够控制进行治理的人们;每一个人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议事日程很小,以致每一个人不仅十分了解大事项,而且也十分了解小事项。
随着政府活动范围和作用的扩大——不论是由于统治面积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还是由于职能范围的扩大——在被治理的人民与进行治理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将变得越来越少。任何一部分公民都不可能十分了解大大扩大了的政府议事日程上的全部事项,甚至不可能十分了解所有主要事项。管理政府所必需的官僚机构成长起来,它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全体公民及其选出的代表们之间。官僚机构既是特殊利益集团借以实现其目标的一种工具,同时本身又是一个重要的特殊利益集团——即第五章中提到的新阶级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目前在美国,只是在乡村、市镇、小城市以及大城市的郊区,说得上公众可以有效而具体地控制政府——而即使在这些地方,公众对政府的控制也只限于那些不是由州和联邦政府委托管理的事情。在各大城市、各个州府和华盛顿,人民的政府不是由人民来控制,而是由不经常露面的官僚集团来控制。
可以想象,没有哪个联邦议员能够看一遍他必须进行表决的所有法令,更不用说分析和研究这些法令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必然要依靠他的许多助手、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议员同事、或者某些其他提供消息的人,来决定如何表决。目前,对于制定具体法令来说,未经选举产生的国会中的官僚肯定要比选举产生的议员具有大得多的影响。
在实施各项政府计划方面,情况甚至更为严重。广泛分布在政府各部门和各种独立机构中的官僚,确实不受公众选出来的代表控制。选举产生的总统、参议员和众议员此来彼去,但文职人员却保留不动。高级官僚非常老练地运用拖拉的办事程序来耽搁和破坏他们不赞成的计划;他们善于以“解释”法令为名颁布各种条例和规章,这些解释事实上巧妙地、有时赤裸裸地改变了原法令的意图;他们善于拖延执行他们不赞成的法令,同时加紧执行他们赞成的法令。
最近,面对日益复杂的和影响广泛的立法,联邦各法院已不再充当公正解释各项法令的传统角色,而是积极参与制定法令和实施法令的工作。因此,它们变成了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而不是斡旋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一个独立部分。
官僚们没有篡夺权力。他们没有故意参与任何一种破坏民主程序的阴谋。权力被强加到他们头上。除了赋予职责外,以任何其他方法从事复杂的政府活动,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当这一做法在负有不同职责的官僚们之间引起冲突时——例如,最近在被委派去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官僚与被委派去促进能源的保护和生产的官僚之间就发生了冲突——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授权另一批官僚去解决冲突——据说,当真正的问题不是拖拉的办事程序而是有吸引力的各种目标之间的冲突时,只要减少拖拉的办事程序就行了。
被赋予职责的高级官僚们,不能设想他们提出或接到的报告、他们参加的会议、他们同其他重要人物进行的冗长的讨论、他们颁布的规章制度——所有这些都是问题本身,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不可缺少的,认为自己比无知的选民或自私自利的企业家更知道应该做些什么。
官僚机构的规模和权力的增长,影响着公民和其政府之间关系的每一个细节。如今如果你有冤屈或者你能从政府措施中发现获取利益的办法,你首先采用的方法很可能是对某个政府官员施加影响,使他作出有利于你的裁决。你也可能求助于你选出的议员,但你求助于他,是要他与一名政府官员相串通,好替你说话,而不是要他支持某项法案。
要办好企业越来越依赖于熟悉华盛顿的情况,依赖于能够影响议员和政府官员。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出现了所谓“旋转门”。在华盛顿当一个时期的官,已成了企业家办好企业必经的学徒期。谋求政府职位,很少是要在政府内干一辈子,而是想同将来可能成为雇主的政府建立联系,了解其内情。虽然防止公务人员舞弊的法律急剧增加,但它们至多只是阻止了人们明目张胆地舞弊。
当某一特殊利益集团试图通过惹人注意的立法活动为自己谋取利益时,它不仅必须给它的要求装点上普遍利益的词句,而且必须使相当一部分不感兴趣的人相信它的要求对公众是有好处的。被认为是明显自私自利的议案很少被通过——例如,虽然卡特总统在得到有关工会对竞选运动的巨大帮助以后表示赞同给海运业以更多特权,但这一企图最近却遭到了失败。保护钢铁工业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据说有利于国家安全和充分就业;向农业提供补贴,据说可以确保食品的可靠供应;国家垄断邮政事业,据说可以加强整个国家的团结,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近一个世纪以前,A.V.迪塞说明了为什么打着普遍利益幌子的花言巧语具有如此巨大的说服力:“州政府的干预,特别是采用立法形式的干预的有益效果,是直接的、立竿见影的,并且可以这样说,是显而易见的,而它的有害效果则是间接的、渐进的,是看不到的。……因此,大多数人必然过于偏爱政府干预。”
当某一特殊利益集团不是通过立法活动而是通过行政程序谋求利益时,戴斯所说的对政府干预的“自然偏爱”便会大大加强。一家卡车运输公司为了得到有利的裁决而求助于州际商务委员会时,往往也打着促进普遍利益的幌子,但谁也不会戳穿这个谎言。除了政府官员外,该公司无需说服任何人。反对意见很少来自那些关心普遍利益而与卡车运输业无关的人。反对意见来自其他有关各方,如托运人或其他卡车运输公司,他们也有自己的打算。披上的伪装确实是薄薄的一层。
法院作用的变化,使官僚机构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发展嘲弄了约翰·亚当斯在马萨诸塞州的宪法草案(1779年)中表达的理想,即建立“一个由法律支配的而不是由人支配的政府”。凡是从国外旅行回来接受过海关彻底检查的人,凡是让国内收入署审核过税单的人,凡是接受过职业安全和卫生管理局的一名官员或联邦各种机构的一大堆官员检查的人,凡是要求过政府机构给予裁决或给予营业执照的人,凡是在工资和价格稳定委员会面前为提高价格或工资作过辩护的人,总之,凡是同政府官员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美国到底有多少法治可言。政府官员理应是我们的仆人。当你隔着办公桌坐在正审核你的税单的国内收入署代表的对面时,究竟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呢?
让我们来看另一个例子。《华尔街日报》(1979年6月25日)最近一篇报道用的大标题是:一家公司的“前任经理支付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费用”。据报道,这位前任经理莫里斯·G.麦吉尔说:“问题不在于我本人是否从这笔交易中得到了好处,而在于一个卸任的经理的责任是什么。打官司是会引起兴趣的,可我却决定不打官司就付清费用,这完全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同证券交易委员会斗争到底的代价是巨大的。”不论胜败麦吉尔先生都必须支付诉讼费。而证券交易委员会内负责同他打官司的那位官员,除了在同事中的声誉会受到影响外,不论打胜还是打败,同他自己都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能够做什么
不用说,凡是想阻止或扭转目前这种趋势的人,都应该反对进一步扩大政府权力和职责范围的新措施,应该促使现有措施的废除和改革,而且应该选出具有这种观点的议员和行政官员。但这不是扭转目前趋势的有效方法。这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会保卫自己的特权,并试图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对政府进行限制。我们面对的将是一条九头蛇,它长出新的头能比砍掉旧的头还快。
我们的开国元勋已经给我们指出了一种较为有希望扭转目前趋势的方法:可以说是搞一揽子交易。我们应该采用自我克制的各种法令,以限制我们企图通过政治渠道追求的目标。我们不应该按照其是非曲直考虑每件事情,而应该制定广泛的规章和条例以限制政府的活动范围。
这种方法的优点已被宪法的第一项修正案很好地说明了。相当一部分议员和选民也许会赞成对言论自由施加某些限制。大多数人很可能赞成禁止纳粹分子、耶稣七日再生派教徒、“耶和华的见证人”派教徒、三K党、素食主义者或任何其他小集团在街头巷尾发表演讲。
第一项修正案的高明之处在于它采用了一揽子交易的方法。该修正案用的普遍原则是:“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之……法律”;它没有按照是非曲直考虑每件事情。大多数人那时支持了它,而我们相信大多数人今天仍然会支持它。当我们处于多数人的地位时,对别人的自由受到干涉,我们每人的感受远远不如自己处在少数人的地位时,不让自由受到干涉来得深切——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总有处于少数人的地位的时候。
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有一项与宪法的第一项修正案相同的法案,来限制政府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权力——一项经济上的“人权法案”,以补充和加强原来的“人权法案”。
把这样一种“人权法案”并入我国的宪法中,这件事本身并不会自行扭转政府越来越大的趋势,或防止这种趋势重新得到发展——它的作用肯定不会超过宪法本身。我国的宪法未能阻止政府权力的增长和集中,以致政府权力的增长和集中远远超出了宪法制定者允许或设想的界限。对于发展和保护一个自由社会来说,一部成文宪法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虽然英国经常只有“不成文”宪法,但它却使自由社会得到了发展。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采用了事实上从美国宪法逐字照抄过去的成文宪法,但它们并没有建成自由社会。一部成文的——或者与此有关的不成文的——一宪法要发挥效力,它必须在一般公众及其领导人中间得到普遍的舆论支持。该宪法必须体现人们已经深信的各项原则,这样,行政部门、立法机关和法院的行为才会自然而然地符合这些原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舆论发生变化时,政策也将随之变化。
然而,我们认为制定和投票通过经济上的“人权法案”,将最有效地扭转政府越来越大的趋势,其原因有二:第一,制定修正案的过程会对制造舆论起很大的帮助;第二,同现在的立法程序相比,颁布修正案将更为直接、更为有效地使上述舆论变成实际政策。
假定赞成新政自由主义的思潮已经达到顶点,那么,在制定这样一个“人权法案”的过程中将会引起全国性的争论,这场争论肯定会使人们的思想转向自由,而不是转向集权主义。这场争论将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大政府的问题及其可能的医治方法。
采用这类修正案的政治过程,将比我们现在的立法和行政结构更为民主,因为它使一般公众得以决定事态的结果。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人民的政府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志行事。每一次民意测验都表明,绝大多数人反对为调整学生中的种族比例用校车接送学生——可是不仅继续用校车接送学生,而且还不断推广这种做法。在就业和高等教育方面实施的种种调整种族比例的行动计划,以及根据结果平等的思想采取的其他许多措施,情况也都是这样。就我们所知,搞民意测验的人从来没有向公众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你的40%以上的收入由政府替你花费,你是否得到了所付款项的等价物?”对于民意测验的结果,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
由于上一节列举的原因,特殊利益集团是在牺牲普遍利益的情况下获得成功的。在大学、新闻单位、特别是联邦官僚机构中成长起来的新阶级,已经成了最有势力的特殊利益集团之一。它不顾公众的普遍反对,并且经常不顾有关法令的约束。总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别人头上。
采用修正案具有加强地方分权制的巨大效能。它要求四分之三的州分别采取行动。甚至新的修正案的提出可以越过国会:宪法第五条规定“国会……应三分之二的州议会的请求,将召集会议以提出修正案。”到1979年中期,已有三十个州要求国会召开会议,以提出要求联邦预算保持平衡的修正案。再有四个州议会提出这种要求,即可达到召开会议所必需的数目,这一前景在华盛顿已经引起了极大惊慌——其原因是:这样一来,华盛顿的官僚机构就被抛在一边。
限制税收和政府开支
采用宪法修正案来限制政府的运动,在税收和政府开支方面已经开展起来了。到1979年初,已经有五个州正式通过了本州宪法的修正案,修正案限制了州政府可以征收的赋税总额,一些州还限制了州政府可以开支的经费总额。同样性质的修正案,在其他一些州中已做好了正式通过的准备工作,在另外一些州里则预定在1979年选举中提出来进行投票表决。剩下的一些州有半数以上正在积极准备通过这类修正案。同我们有联系的一个全国性组织“全国税收限制委员会”(NTLC),作为情报交换所和某几个州的行动协调者正在起作用。1979年中期,该组织在全国拥有约二十五万名会员,而且会员人数正在急剧增加。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有两项重要的事态发展。一个是各州议会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去委托国会召集全国性会议以提出平衡预算的修正案——这最初是由全国纳税人联盟发动的,该联盟于1979年中期在全国拥有的会员超过十二万五千人。另一事态发展是,人们要求通过限制联邦开支的修正案,该修正案是在全国税收限制委员会倡议下起草的。起草委员会(我们两人都是该委员会委员)包括了律师、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州议员、企业家以及各团体组织的代表。该委员会起草的修正案已被提交给了国会参众两院,全国税收限制委员会正在开展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来支持它。
在州和联邦两类修正案背后的基本思想,是纠正我们现有结构中的缺点,在这种结构下面,民主选出的议员,投票赞成的开支数额要多于大部分选民认为合适的数额。
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上述结果是由赞成特殊利益的政治偏见造成的。目前确定政府预算的办法,是把批准用于各项计划支出加在一起。与某项计划有特殊利益的少数人,花钱并努力活动使该计划得以通过;而大多数人即使对该计划有了解,而且每个人要为计划支付若干美元,也不会认为花钱或努力活动反对该计划是合算的。
多数人的确在实行统治。但这是有点特殊性质的多数。它是由许多具有特殊利益的少数人的集团构成的。当选国会议员的方法,是把各占你的选民的,比如说,2%或3%的诸集团集中起来,这些集团中的每一个集团都强烈地关心着一个特殊问题,该问题同你的其余选民几乎没有关系。假如你答应支持某个集团的问题,它将乐意投你的票,不管你对其他问题持何种态度。把足够的这类集团集合起来,你将拥有51%的多数。这就是统治着我国的互投赞成票的多数。
上面提出的修正案将限制议员——不论是州议员还是联邦议员——受权拨付的款项总额,从而改变议员起作用的条件。这些修正案将预先限定政府的预算,就象我们每一个人的预算都受到限制一样。许多与特殊利益有关的立法是不值得追求的,但它们的坏处决不至于那么明显,也并不是那么一无是处。相反,每一种措施都将被描述为服务于一个高尚的目标。问题是高尚的目标太多了,数也数不尽。当前,议员在反对“高尚的”目标方面往往处于劣势。假如他提出反对的理由,说某一高尚的目标将提高税收,那他将被扣上反动分子的帽子,说他为了卑鄙的唯利是图的原因而不顾人民的需要——毕竟,这个高尚的目标将只需要把每个人的税款提高几美分或几美元。这个议员将处于有利得多的地位,如果他能够说:“不错,你的目标是高尚的,可是我们的预算是有限的。为你的目标花更多的钱意味着为减少其他目标得到的钱。这些目标当中哪一个应该被削减?”结果将会要求各个特殊利益集团,为了从一个固定的馅饼中分得较大份额而彼此竞争,而不是他们能彼此勾结起来牺牲纳税人的利益,把馅饼做得越来越大。
因为各州无权印制钞票,所以州政府的预算可以通过控制可征收的税款总额加以限制,这是各州已经正式通过或者已经提出的大多数修正案业已采用的方法。联邦政府能够印制钞票,因此限制税收不是一种有效的办法。这就是我们的修正案为什么要限制联邦政府的总开支的原因,而不论资金是怎样筹集的。
限额——不论是对税收还是对政府开支——将主要根据州或全国的总收入来规定,如果政府开支等于限额,政府的开支作为收入的一部分将保持不变。这将阻止政府越来越大的趋势继续发展,而不是扭转这种趋势。然而,限额也将有助于扭转政府越来越大的趋势,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如果哪一年的政府开支不等于限额,则适用于以后年份的限额会更低。而且,提出的联邦修正案要求降低政府开支在州或全国的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如果通货膨胀年率超过3%的话。
其他宪法条款
我们收入中政府所花费的那一部分的逐渐减少,对于建立一个较为自由、较为强大的社会来说,将是重要的贡献。但这仅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步骤。
政府对我们的生活进行的许多最有破坏性的管理,并不要政府花许多钱,例如:征收关税,实行物价和工资管制,颁发职业执照,对工业实行管制,颁布保护消费者的法令等。
对付所有这些政府管制的最有成效的方法,同样是颁布限制政府权力的一般性法规。到目前为止,制定适当法规的工作仍未受到人们的重视。任何法规在其能被认真地采用以前,需要由具有各种不同利益的人进行的彻底审查,需要限制税收和政府开支的修正案已得到的那种认识。
作为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我们概述一下看来是合乎需要的几项修正案。我们强调这些例子是尝试性的,主要目的是在这一基本尚未探索过的领域中,激励进一步的思考和进一步的工作。
国际贸易
宪法现在规定:“未经国会同意,各州不得对进口商品或出口商品课以任何进口税或出口税;惟在执行该州之检查法律上有绝对必要者,不在此限。”修正案可能规定如下:
国会不得对进口商品或出口商品课以任何进口税或出口税,惟在执行其检查法律上有绝对必要者,不在此限。
以为现在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修正案,那是不切实际的。然而,要通过废除个别关税获得 贸易自由,如果说有不同之处的话,则是更加不切实际。对全部关税采取措施,可以使我们大家作为消费者的利益联合起来,以反对我们作为生产者分别具有的那种特殊利益。
工资和物价管制
正如我们在几年前写道的:“假如美国有一天屈服于集体主义,屈服于政府对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管制,那将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者在论战中取得了胜利,而是因为工资和物价管制。”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指出的,价格传送消息——沃尔特·里斯顿通过把价格描述为言论的一种形式,已经非常恰当地解释了这一点。而在自由市场上决定的价格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在此我们需要有同宪法的第一项修正案极为相似的条文:
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以剥夺商品或劳务的卖者对其产品及劳务定价的自由。
职业执照的颁发
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比我们可能从事的工作对我们的生活具有更大的影响。在这个领域里 放宽自由选择就要求限制各州的权力。在此,我们需要有我国宪法正文里禁止各州采取某些行动的条款,或者是第十四项修正案。一个建议是:
各州不得制定或施行剥夺合众国公民从事他所选择的工作或职业的权利的任何法律。
多用途的自由贸易
修正案前面的三项修正案可以由一项修正案来代替,这项修正案可以仿效我国宪法的第二项修 正案(它确保人们保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人们在相互同意的条件下买卖合法的商品和劳务的权利,国会和任何州均不得侵犯之。
税收
按照一致同意的看法,个人所得税亟需改革。据说这种赋税根据“支付能力”征收的,对富人较重而对穷人较轻,并且考虑到了每个人的特殊情况。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税率在官方文件上被分成许多等级,从14%到70%。然而税法的漏洞如此之多,特免规定又五花八门。以致高额税率差不多完全成了装璜门面的东西。对高于个人免征额的全部收入(除真正的职业开支外,不允许有其他扣除),实行一种一刀切的低额税率——低于20%——会比现有不实用的结构给政府带来更多的收入。纳税人的境况会好一些——因为他们可以省掉因避免所得税而花的费用;经济情况也会好一些——因为税收考虑在资源分配中将起较小的作用。唯一吃亏的人是律师、会计、文职人员以及议员们——他们将不得不从事比填写各种税单、发现税收漏洞并且试图堵塞漏洞等工作更富有成效的活动。
公司所得税也是有很大缺点的。它是一种隐蔽的赋税,公众在所购买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中不知不觉地纳了税。这种赋税对公司所得征两次税——一次是对公司课税,一次是收入分配后对股东课税。它不利于资本投资,从而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它应该被废除。
尽管左派和右派一致认为,应该降低税率,减少漏洞并取消双重课税制,但这种改革却不能通过立法程序来完成。左派担心假如他们同意较低的税率和较少的纳税等级以换取消灭漏洞,新的漏洞不久就会出现——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右派担心假如他们同意消灭漏洞以换取较低的税率和较少的纳税等级,更不合理的纳税等级不久就会出现——他们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例,说明只有宪法修正案可以使各方达成体面的妥协。这里所需要的修正案必须废除现有的批准所得税的第十六项修正案,而代之以下面一段话:
国会有权课征个人所得税,不必问其所得之来源,其收入不必分配于各州,亦不必根据人口普查与统计,只是必须对超过职业与商业开支以及固定数额的个人津贴的一切收入施以同一税率。“个人”一词不包括公司和其他法人。
稳定的货币
当初颁布宪法时,国会被授权“铸造货币,厘定本国货币及外币之价值”,指的是商品货币:说明美元应为一定克数重量的白银或黄金。美国革命期间以及更早一些时候各殖民地内纸币的膨胀,使得宪法制订者否定各州有权“铸造货币;发行信用票证(即纸币),使用金银币以外之物以作清偿债务的货币。”宪法未说明国会是否有权批准政府发行纸币。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根据第十项修正案的规定,政府发行纸币是违反宪法的。第十项修正案规定“本宪法所未授予合众国……之权力,皆分别由各州或由人民保留之”。
南北战争期间,国会授权政府发行美钞,并宣布美钞为偿付一切公私债务的合法货币。南北战争以后,在一系列有关美钞的著名讼案中,最高法院在审理第一个讼案时曾宣布发行美钞是违反宪法的。“使人摸不着头脑的是,这项裁决是由首席法官萨蒙·P.蔡斯公布的,正是在他担任财政部长时发行了第一批美钞。他不仅公布了这项裁决,而且还以首席法官的身份,宣布自己应对担任财政部长时的违反宪法的行为负责。”
随后,扩大了的和重新组成的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多数推翻了第一个决定,断言使美钞成为合法货币是合乎宪法的,首席法官蔡斯当时是持反对意见的法官之一。
恢复金币本位制或银币本位制既行不通也不合乎需要,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使货币保持稳定。目前最好的方法,是要求货币当局把货币数量的增长率保持在一个固定的变动范围之内。修正案的起草是格外困难的,因为它同有关的制度结构联系非常紧密。修正案也许应该这样写:
国会有权批准政府以通货或记帐的形式发行无息债券,如果流通中的美元总额的年增长率不超过5%和不低于3%的话。
也许应该附带这样一条规定,即如果爆发战争,从而使政府停止或延期支付每年应清偿的债务时,国会参众两院各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或者同样有资格的多数,可以撤销上述要求。
免遭通货膨胀的损害
假如前面一项修正案被通过并被严格执行,那将结束通货膨胀并确保物价水平相对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将不需要采取其他措施来阻止政府未经允许而随意征税,因而也就不存在因征税而引起的通货膨胀。然而,那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得到人们广泛支持的,将是使政府搞通货膨胀无利可图的修正案。它比一个较为专门和容易引起争论的稳定货币的修正案,采用起来容易得多。实际上,所需要的是引申第五项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凡私有财产,非有相当补偿,不得收为公有。”
凡是其货币收入刚好赶上通货膨胀的步伐然而被推升到较高纳税等级的人,可以说未经正当手续而被剥夺了财产。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拒绝偿付政府公债的一部分实有价值,就是未经相当补偿而把私有财产收为公有。
有关的修正案可以规定:
美国政府和其他各方之间以美元表示的所有合同,以及列入联邦各种法令中的美元金额,应根据上一年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逐年加以调整。
和稳定货币的修正案一样,这项修正案由于涉及一些技术问题,起草起来也是很困难的。
各种技术细节将不得不由国会来规定,例如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指数反映“一般物价水平”。但是修正案可以阐明基本原则。
到这里,全部工作并未完成——本来我们打算根据人权法案的十项修正案提出十项新的修正案,但我们只提出了七项,还有三项没有完成。而且我们提出的新修正案的措辞,不仅需要研究宪法的法律专家仔细推敲,而且也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们仔细推敲。但是,我们相信,这些修正案至少告诉人们,采用制定新法律的方法解决问题是大有希望的。
结论
人类自由和经济自由这两种思想的携手并进,在美国结出了最丰硕的果实。在我们的头脑里,这些思想仍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我们大家都浸透了这些思想。它们是我们生存的真实依靠。可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偏离了它们。我们忘记了一条基本的真理,即对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权力的集中,无论是集中在政府手里,还是集中在任何其他人手里。我们使自己相信,只要权力的授予是出于高尚的目的,就不会带来损害。
幸运的是,我们醒悟过来了。我们再次认识到一个管制过严的社会的危险,终于懂得好的目标可以被坏的方法所歪曲,懂得了依靠人民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自由地管理他们的生活,乃是使一个伟大社会发挥其全部潜力的最可靠的方法。
同样幸运的是,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仍然可以自由选择走哪条道路——或者是继续沿着我们正在走的道路进一步扩大政府,或者是悬崖勒马,调转方向。
本节内容概述
我们应该采用自我克制的各种法令,以限制我们企图通过政治渠道追求的目标。我们不应该按照其是非曲直考虑每件事情,而应该制定广泛的规章和条例以限制政府的活动范围。
一部成文的——或者与此有关的不成文的——一宪法要发挥效力,它必须在一般公众及其领导人中间得到普遍的舆论支持。
政府对我们的生活进行的许多最有破坏性的管理,并不要政府花许多钱,例如:征收关税,实行物价和工资管制,颁发职业执照,对工业实行管制,颁布保护消费者的法令等。对付所有这些政府管制的最有成效的方法,同样是颁布限制政府权力的一般性法规。
1.国会不得对进口商品或出口商品课以任何进口税或出口税,惟在执行其检查法律上有绝对必要者,不在此限。
2.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以剥夺商品或劳务的卖者对其产品及劳务定价的自由。
3.各州不得制定或施行剥夺合众国公民从事他所选择的工作或职业的权利的任何法律。
4.人们在相互同意的条件下买卖合法的商品和劳务的权利,国会和任何州均不得侵犯之。
对高于个人免征额的全部收入(除真正的职业开支外,不允许有其他扣除),实行一种一刀切的低额税率——低于 20%——会比现有不实用的结构给政府带来更多的收入。纳税人的境况会好一些——因为他们可以省掉因避免所得税而花的费用;经济情况也会好一些——因为税收考虑在资源分配中将起较小的作用。唯一吃亏的人是律师、会计、文职人员以及议员们——他们将不得不从事比填写各种税单、发现税收漏洞并且试图堵塞漏洞等工作更富有成效的活动。
公司所得税也是有很大缺点的。它是一种隐蔽的赋税,公众在所购买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中不知不觉地纳了税。这种赋税对公司所得征两次税——一次是对公司课税,一次是收入分配后对股东课税。它不利于资本投资,从而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它应该被废除。
5.国会有权课征个人所得税,不必问其所得之来源,其收入不必分配于各州,亦不必根据人口普查与统计,只是必须对超过职业与商业开支以及固定数额的个人津贴的一切收入施以同一税率。“个人”一词不包括公司和其他法人。
恢复金币本位制或银币本位制既行不通也不合乎需要,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使货币保持稳定。目前最好的方法,是要求货币当局把货币数量的增长率保持在一个固定的变动范围之内。
6.国会有权批准政府以通货或记帐的形式发行无息债券,如果流通中的美元总额的年增长率不超过5%和不低于3%的话。
也许应该附带这样一条规定,即如果爆发战争,从而使政府停止或延期支付每年应清偿 的债务时,国会参众两院各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或者同样有资格的多数,可以撤销上述要求。
免遭通货膨胀的损害
7.美国政府和其他各方之间以美元表示的所有合同,以及列入联邦各种法令中的美元金额,应根据上一年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逐年加以调整。
和稳定货币的修正案一样,这项修正案由于涉及一些技术问题,起草起来也是很困难的。各种技术细节将不得不由国会来规定,例如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指数反映“一般物价水平”。但是修正案可以阐明基本原则。
我们使自己相信,只要权力的授予是出于高尚的目的,就不会带来损害。
幸运的是,我们醒悟过来了。我们再次认识到一个管制过严的社会的危险,终于懂得好 的目标可以被坏的方法所歪曲,懂得了依靠人民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自由地管理他们的生活,乃是使一个伟大社会发挥其全部潜力的最可靠的方法。
附录
附录一1928年的社会党纲领
以下是1928年社会党纲领中经济政策的条目,括号内的文字说明了实施这些政策的情况。下面列举的包括全部经济条目,但不是每一条都是全文。
1.“将自然资源收归国有,从煤矿和水域开始,特别是博尔德水坝和马斯克尔海滩。”(博尔德水坝和马斯克尔海滩现在都是联邦政府负责的工程。博尔德水坝已改名为胡佛水坝。)
2.“建立一个公有的巨大动力系统,在这个系统下,联邦政府应与州和市政府合作按成本把电力销售给人民。”(已建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3.“将铁路和其他交通运输工具收归国有并对其进行民主管理。”(铁路客运已由全国铁路客运公司全部国有化。某些货运也已由联合铁路公司国有化。联邦电讯委员会控制了电话、电报、无线电和电视通讯。)
4.“在防洪、救洪、造林、灌溉和垦荒方面实施充分的国家计划。”(政府为这些目的开支的经费现在达好几十亿美元。)
5.“扩大所有公共工程,并实施一项长期的公共工程计划,以立即给失业者以政府的救济。”(本世纪三十年代,直接实施这类计划的机构是工程进度管理署和公共工程局;现在这方面的计划多种多样,数不胜数。而由此雇用的人都按小时计工,工资由真正的工会确定。”(戴维斯-培根法案和沃尔什-希利法案要求政府合同的承包人支付“通行的工资”,一般解释为最高的工会工资。)
6.“向州和市政府提供进行公共工程的无息贷款,并采取能减轻广泛困苦的其他措施。”(现在联邦政府给予州和地方政府的补助费每年共达几百亿美元。)
7.“建立一个失业保险系统。”(社会保险系统的一部分起到了这个作用。)
8.“与各城市的劳工联合会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增加政府开办的职业介绍所。”(美国就业局和所属州就业局管理着一个约有二千五百个地方就业办事处的系统。)
9.“建立健康和意外事故保险系统以及养老金和失业保险系统。”(社会保险系统的一部分起到了这个作用。)
10.“缩短工作日”并“保证每个工人每周有不少于两天的假日。”(在这方面,工资和工作时间法已作了规定,要求每周四十小时以外的工作按加班计算工资。)
11.“通过一项全面禁止雇用童工的联邦修正案。”(目前国会还没有通过这样一项修正案;但其要点已体现在各有关法令中了。)
12.为了囚犯及其家属的利益,取消对合同制下的囚犯的残酷剥削,代之以监狱内的工业合作组织和工场。”(目前已部分达到了这一目标。)
13.“增加对高收入阶层征收的赋税,提高公司税和遗产税,所得用于老年补助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险。”(1928年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为25%;1978年为70%;1928年公司税率为12%,1978年为48%;1928年最高的联邦地产税率为20%,1978年为70%。)
14.“对所有用于投机的土地的年租金征税,所得用于政府拨款。”(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一目标,但财产税确实有大幅度增加。)
附录二限制联邦开支宪法修正案草案
联邦修正案起草委员会起草
主席W.C.斯塔莱宾
全国限制税收委员会召集
主席Wm.F.里肯巴克;会长刘易斯·K.尤勒
第一节保护人民,反对政府加给过重的负担,促进健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美国政府的总支出应有限制。
(1)任何财政年度总支出的增长率,不得超过较该财政年度开始前的一个日历年的名义国民生产总产值的增长率。总支出应包括预算和预算外的开支,不包括公债的偿还和紧急开支。
(2)如果某一财政年度开始前的一个日历年的通货膨胀率超过3%,则允许该财政年度总支出除通货膨胀率外的增长幅度应减少四分之一。通货膨胀率应按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之间的差额计量。
第二节当任何一个财政年度美国政府的总收入超过总支出时,其余额应用于减少美国的公债,直到这种债务被消灭。
第三节在总统宣布紧急状态之后,国会可以以两院的三分之二多数表决,授权拨出超过该财政年度限额的特定数量的紧急开支。
第四节对总支出的限制,可以由国会参众两院四分之三多数表决并经多数的州立法部门批准,作特定数量的改变。改变应自批准后的财政年度生效。
第五节在本条款得到批准后的头六年的每一年内,给予州和地方政府的补助费总额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不得小于批准前的三个财政年度的数额。在那以后,如果补助费在总开支中少于那一数额,则应对总支出的限额作相应减少。
第六节美国政府不应直接或间接要求州或地方政府从事额外的或扩大的活动,而不给予必要的补偿。
第七节实施本条款的办法,是由一个或更多个国会议员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提出起诉(其他人没有此项权力)。诉讼应指定美国财政部长为被告。当法院下令实施本条款的规定时,美国财政部长有权过问美国政府的任何单位或机构的支出。法院的指令不应特别指明某项支出照付或削减。遵照法院指令对支出的调整,不得迟于法院指令发出后三个整财政年度。
1979年1月30日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老版本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货币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自由选择》一书是作者在1979年的新著,它本来是一套连续播放十个星期的同名电视节目的讲稿,后经作者对讲稿进行修订补充和润饰而成书。
弗里德曼于1912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市,1932年在拉特格斯大学毕业,1933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48年起任芝加哥大学教授,还担任过剑l桥大学富尔布特讲座讲师、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他还是美国《经济计量学》杂志编辑部的成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员、皮莱林学会会长,被选为1967年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1980年曾来我国访向。
弗里德曼曾在美国资源委员会、美国财政部赋税研究署和美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等政府机构担任经济专家的工作,并且是1969—1971年尼克松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现在又成为参与制订里根总统的经挤政策的有影响的重要人物之一。
弗里德曼出版了许多经济学论著,主要的有:《自由职业收人》(与西蒙·库兹涅茨合著,1946)、《实证经济学论文集》(1953)、《消费函数理论》(1957),《货币稳定方案》(1959)、《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价格理论:一个假定题目》(1962)、《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与安娜·吉·希沃芝合著,1963)、《通货膨胀:原因与后果》(1963)、《国际收支:自由汇率对伸缩汇率》(与罗伯特·弗·鲁萨合著,1967)、《美元与逆差: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与国际收支》(1968)、《货币最优数量和其他(论文集)》(1969)、《货币分析的理论结构》(1971)、《经挤学家的抗议》(1972)、《失业还是通货膨胀:对菲利昔斯曲线的评价》(1975)、《价格理论》(1976)和《自由选择》(1979)。
《自由选择》是由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夫人罗斯·弗里德曼共同署名的合著,他们用通俗的、为广大读者所容易理解的说明方法,阐述弗里德曼多年以来一直鼓吹的贷币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中心内容是揭露国家干预经济的种种弊端,暴露出所谓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括实质上是如何的不自由和不平等.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缩小国家机构,反对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括滥事干预;反对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反对国家的经济调节、社会福利,经济管制和保护贸易措施,反对工会运动,主张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为特色的国内外经济政策,让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整个经济生活,提出所谓回到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政策中去。他们认为,通过市场的作用可以利用人们利己的动机来为广泛的社会目的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包括“负所得税”、“初级和中级教育凭单”等等具体主张。在进行有关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时,他们提出了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处方——即认为经济中存在着所谓自然失业率,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相互交替的关系,用通货膨胀来应付失业或用失业来应付通货膨胀都是无效的,从而他们主张忍受一个时期较高的失业率,而用稳定贷币增长率的办法来医治通货膨胀。
弗里德曼这一著作是以他多年来对美国经济问题和美国货币史的研究为基础的。由于他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起就对当时盛极一时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提出挑战,因而书中在揭露西方世界实行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和国家干预政策的恶果方面有不少经过整理的材料,可供我们在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质,了解西方世界所面临的高赋税、高失业、高通货膨胀率等实际状况时参考。
但必须严肃指出,在《自由选择》一书中,弗里德曼在有的地方把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权和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相提并论,有的地方甚至把我国说成是恐怖国家,这是非常错误的;而弗里德曼的经济理论的基础——现代货币数量论,也是不科学的。
新版本译后记
《自由选择》是由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夫人罗斯·弗里德曼共同署名的合著,他们用通俗的、为广大读者所容易理解的说明方法,阐述弗里德曼多年以来一直鼓吹的贷币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中心内容是揭露国家干预经济的种种弊端,暴露出所谓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括实质上是如何的不自由和不平等.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缩小国家机构,反对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括滥事干预;反对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反对国家的经济调节、社会福利,经济管制和保护贸易措施,反对工会运动,主张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为特色的国内外经济政策,让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整个经济生活,提出所谓回到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政策中去。他们认为,通过市场的作用可以利用人们利己的动机来为广泛的社会目的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包括“负所得税”、“初级和中级教育凭单”等等具体主张。在进行有关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时,他们提出了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处方——即认为经济中存在着所谓自然失业率,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相互交替的关系,用通货膨胀来应付失业或用失业来应付通货膨胀都是无效的,从而他们主张忍受一个时期较高的失业率,而用稳定贷币增长率的办法来医治通货膨胀。
【按:老版本最后的出版说明体现出十足的求生欲,据译者本人在豆瓣上的吐槽出版社删改太过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