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孔门理财学
史记平准书
史记货殖列传
食货志
自由选择——个人声明
- 简介
- 概述
- 推荐序 作为目的和手段的自由
- 出版序言
- 引言
- 第1章 市场的力量
- 第2章 管理的专横
- 第3章 危机的解析
- 第4章 从摇篮到坟墓
- 第5章 生而平等
- 第6章 我们的学校出了什么问题?
- 第7章 谁在保护消费者
- 第8章 谁在保护工人
- 第9章 通货膨胀的对策
- 第10章 潮流在转变
- 附录
- 老版本出版说明
- 新版本译后记
简介
英文名: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作者:Milton Friedman & Ross Friedman
所选中文翻译版本:商务印书馆西元1982-05出版版本、机械工业出版社西元2019年10月重印版
概述
自由市场经济才能实现繁荣和自由。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政府应让市场经济自由运作不要干预,政府唯一的经济任务是维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
启示如下:
实行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单一低税制、积极不干预、无为而治、藏富于民、民富国富
限制政府权力才能保障民众的自由。
推荐序 作为目的和手段的自由
自由选择和自由贸易能比政府更有效地提升公众的福利。
出版序言
谁要是在一个晚上(或甚至十个晚上,每晚一小时)就被人所说服,那他肯定不是真的被说服、他会因为同另外一个持相反意见的人呆一晚上而改变看法。唯一真正能说服你的人是你自己。没事儿的时候,你脑袋里必须翻来覆去地捉摸这些问题,必须细细咀嚼许多论点,这样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你的临时选择才会变成坚定的信念。
引言
自从欧洲人首次向美洲殖民——1607年在詹姆斯敦,1620年在普利茅斯——以来,美国就成了一块磁石,吸引着人们,有来冒险的,有从暴政下逃出来的,或者干脆就是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谋求较好的生活的。
开始时是涓涓细流,但在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后,细流慢慢变粗,到十九世纪就成了一股洪流。千百万人不堪忍受苦难和暴政,被自由和富裕的生活所吸引,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来到了美国。
他们踏上美国国土时,并没有发现黄金铺的路;生活也不象从前想象的那么好过,但他们确实获得了自由,获得了充分发挥他们才能的机会。靠着苦干、精明、节俭和老天爷的保佑,大多数人实现了自己的希望和梦想,诱使他们的亲戚朋友也来参加他们的奋斗行列。
美国的历史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同时发生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发生奇迹,是因为美国人把两套思想付诸了实践——说来也巧,这两套思想都是在1776年公诸于世的。
一套思想体现在《国富论》里,这部伟大的杰作使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成了现代经济学之父。该书分析了市场制度为什么能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经济领域里生产我们的衣、食、住所必需的广泛合作结合起来。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见解是:参加一项交易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而且,只要合作是严格自愿的,交易双方得不到好处,就不会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和对自由的侵犯来促使人们合作。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只盘算他自己的得益”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去达到一个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目的。对于社会来说,同他的盘算不相干并不总是坏事。他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促进社会的利益,常常比他实在想促进时还更有效果。我没听说过,那些装作是为公众的利益做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第二套思想体现在独立宣言中,该宣言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表达了他的同胞的普遍情绪。它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这是历史上按照人人有权追求自己的价值的原则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创而平等,耶和华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用更为偏激和绝对的话说:
人类有理由为之个别地或集体地干涉任何一部分人的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是自我保护。……对文明社会的某一成员正当地强制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防止他对别人进行伤害。人类自己的长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不是足够的理由。……任何人的行为对社会负责的部分只是关系到别人的部分。就其仅仅关系他自己的那部分来说,他的独立按道义说是绝对的。对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身心,个人就是主宰。
美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实现独立宣言中的各项原则而奋斗的历史——开头是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最后通过一场流血的内战而解决),后来是促进机会均等的斗争,最近则是力图达到收入均等的斗争。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如果人们在没有高压统治和中央指挥的情况下能够相 互合作,那么这可以缩小运用政治权力的范围。此外,自由市场通过分散权力,可以防止政治权力的任何集中。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手里,肯定会给人民带来暴政。
十九世纪,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黄金时代。美国甚至比英国更繁荣。它以清白的历史开始:阶级和等级的余毒较少;政府的限制较少;而土地则较为肥沃,人们可以去努力开发,去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还有一片尚未开发的大陆,等待着人们去征服。
自由的繁殖力在农业上表现得最为显著。在通过独立宣言的时候,只有不到三百万欧洲人和非洲血统的黑人(即不包括印第安土著)占据着沿东海岸的一块狭长地带。当时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活动。要用95%的劳力来养活全国的人口和提供粮食剩余,以换取外国货物。今天,只用不到5%的劳力就能养活二亿二千万居民并提供大量的粮食剩余,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
这一奇迹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显然不是政府的中央指导,因为俄国及其卫星国、大陆中国、南斯拉夫和印度等国目前虽然依靠中央指导把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劳力用于农业,但仍然时常要依赖美国的农业来避免大规模的饥荒。在美国农业获得迅速发展的大部分时期,政府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可以得到土地——但却是些以前什么也不出产的地。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建立了一些由政府赠与土地的农学院,它们依靠政府的资助传播情报和技术。但是毫无疑问,美国农业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在自由市场上发挥作用的个人积极性。这个自由市场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当然,可耻的奴隶制下的奴隶是无法进入自由市场的。而最迅速的增长是在废除了奴隶制以后。千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自由地为自己而劳动,其中有些是独立的农民或工商业者,有些则按照相互协议的条件为别人工作。他们可以自由地试验新技术——试验失败的风险由自己承担,试验成功的好处归自己所有。他们得到政府的帮助极少。更重要的是,他们遭到政府的干涉极少。
政府开始在农业中起主要作用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及其以后的时期。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限制产量,以保持人为的高价。
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是靠了在自由的刺激下同时发生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了使农业发生革命的新机器。反过来,工业革命又依赖农业革命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工业和农业手携手地共同向前迈进。
斯密和杰斐逊都把政府权力的集中看作是对老百姓的巨大威胁;他们认为,不论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护公民免受政府的专制统治。这就是弗吉尼亚权利宣言(1776年)、美国权利法案(1791年)以及美国宪法中规定的三权分立的目的;也是英国十三世纪颁布大宪章和十九世纪末改革法律机构的推动力。在斯密和杰斐逊看来,政府应该是仲裁者,而不应是当事人。杰斐逊的理想,正象他在1801年的首次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那样,是建立“(一个)开明而节俭的政府,它将制止人们互相伤害,但仅此而已,在其他一切方面将放手让人们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从事自己的事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成功,减少了它对后来的思想家们的吸引力。十九世纪后期的政府受到严格限制,集权甚少,不危及老百姓。但另一方面,它的权力也很少,使好人做不了好事。在一个并非尽善尽美的世界上,还有许多罪恶。的确,正是社会的进步使残余的罪恶显得更加可恶可憎。象往常一样,人们认为事情必然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们忘记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对自由的威胁,心里想的只是更为强大的政府所能做的好事,认为只要权力掌握在“好人”手里,政府就会做好事。
这些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影响英国政府的政策。而且被越来越多的美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但直到三十年代初期的大萧条时,才开始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有所影响。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指出的,大萧条是政府在金融领域中的失败造成的。在金融领域,政府自建国初期以来就一直在行使权力。但是,政府对于大萧条的责任,当时和现在都没被认识。相反,人们却普遍认为大萧条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造成的。这个神话使公众也加入了知识分子的行列,改变了过去对于个人和政府的看法。原来人们强调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现在却强调个人应象象棋中的小卒那样由外界力量来摆布。原来认为政府的作用是充当仲裁者,防止人们互相强迫,现在却认为政府应充当家长,有责任迫使一些人帮助另一些人。
这种看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支配了美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各级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地方政府的权力和本来由地方政府掌管的事业,被越来越多地移交给了中央政府。政府以安全和平等为名,越来越经常地把从某些人那里得到的东西给与另一些人。政府制定出了一项又一项的政策来“管理”我们“对目标和事业的追求”,把杰斐逊的名言完全颠倒了过来(见第七章)。
人们本来是出于好意,是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但现在即便是最起劲地鼓吹福利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在政府活动的领域,正如在市场中一样,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它的作用正好同斯密的那只手相反:一个人如果一心想通过增加政府的干预来为公众利益服务,那他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增进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私人利益。这一结论将在本书一些章节考察政府行使权力的那些领域时得到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无论是建立安全(第四章)或平等(第五章),或是促进教育(第六章),保护消费者(第七章)或工人(第八章),还是防止通货膨胀和促进就业(第九章),总之,在政府行使权力的一切领域,都证明了这一点。
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迄今为止,“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上的大错误,使事情趋于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亚当·斯密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强大得足以克服活动在政治领域里的那只手造成的麻痹作用。
近来的经历——经济增长缓慢,生产率下降——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我们继续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政府,继续把权力授给公务人员这样一个“新的阶级”,让他们代表我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收入,那么,个人的独创性是否还能克服政府控制的麻痹作用。一个日益强大的政府迟早将摧毁自由市场给我们带来的繁荣,摧毁独立宣言庄严宣布的人类自由。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我们许多人预料的要早。
我们还没有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仍有自由选择的机会,是继续沿着“通向奴役的道路”(这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为他的一本意义深刻而颇有影响的书起的名字)疾驰下去,还是加紧对政府的限制,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人们自觉自愿的合作来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是听任黄金时代结束,而沦入大多数民族过去一直遭受而且目前仍在遭受的专制统治和苦难呢?还是运用我们的智慧、先见之明和勇气来改弦更张,记取经验教训,而从“自由的复兴”中得到好处?
如果我们要作出明智的抉择,我们就必须了解我国制度的运行所依赖的基本原则,既要了解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原则(见第一章),又要了解杰斐逊提出的政治原则(见第五章)。斯密的经济原则告诉我们一个复杂的、有组织的、顺利运行的制度为什么能在没有中央指导的情况下获得发展并繁荣兴旺,同时告诉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不采用强制性手段而使人们相互协作。我们必须懂得为什么试图以中央指导代替合作会造成那么多损害(第二章)。我们也必须懂得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密切关系。
幸好,潮流在转变。在美国、英国、西欧各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里,人们对政府作用的增大带来的威胁越来越有所认识,对所遵循的政策越来越不满。这一转变不仅反映在舆论上,也反映在政治领域里。对于我们的议员们来说,唱不同的调子乃至采取不同的行动,正在变成政治上有利的事。我们正经历着公众舆论的另一次重大改变。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使人们更加相信个人的积极性和自愿的合作,而不是转向完全集体主义的另一极端。在本书最后一章里,我们探讨为什么在一个按说是民主的政治体制里,特殊利益会压倒一般利益,探讨我们能做些什么来纠正造成这种结果的制度上的缺点,探讨怎样才能既限制政府又使它能够履行自己的主要职能。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防御外来敌人的侵略,确保我们的每一个同胞不受其他人的强迫,调解我们内部的纠纷,以及使我们能一致同意我们应遵循的准则。
本节内容概述
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见解是:参加一项交易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而且,只要合作是严格自愿的 ,交易双方得不到好处,就不会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和对自由的侵犯来促使人们合作。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只盘算他自己的得益”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去达到一个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目的。对于社会来说,同他的盘算不相干并不总是坏事。他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促进社会的利益,常常比他实在想促进时还更有效果。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如果人们在没有高压统治和中央指挥的情况下能够相互合作,那么这可以缩小运用政治权力的范围。此外,自由市场通过分散权力,可以防止政治权力的任何集中。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手里,肯定会给人民带来暴政。
在斯密和杰斐逊看来,政府应该是仲裁者,而不应是当事人。杰斐逊的理想,正象他在 1801 年的首次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那样,是建立“(一个)开明而节俭的政府,它将制止人们互相伤害,但仅此而已,在其他一切方面将放手让人们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从事自己的事业。”
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迄今为止,“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上的大错误,使事情趋于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
一个日益强大的政府迟早将摧毁自由市场给我们带来的繁荣,摧毁独立宣言庄严宣布的人类自由。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防御外来敌人的侵略,确保我们的每一个同胞不受其他人的强迫,调解我们内部的纠纷,以及使我们能一致同意我们应遵循的准则。
附录美国《60分钟节目》调查走线的中国“润人”
结合知乎问题美国《60分钟节目》调查走线的中国“润人”,准备遣返3.6万人,但中国一个都不接收。他们的结局会如何?看充满这种行为社会主义特色。
作者:Auguard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43239628/answer/3389754461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以下是一些有意思的提要
1.去年有250W起接收或者驱离来自墨西哥偷渡客的事件,其中中国移民是增长最快的群体。
2. 在他们团队摄影的4天内,有近600人从文章中的这个漏洞中进入美国。
3. 去年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案的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有3.7W人,他们告诉栏目组他们来到美国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原因。
4. 节目组问这些人怎么知道这个漏洞的,他们说在抖音上有全流程分享。
5. 节目组被其中的中产阶级,以及走线人的秩序所惊讶到了,而且他们与边管人员很配合(而且他们带着手机,笔记本电脑,穿的也很好)。
6. 漏洞所在地归于75岁的Jerry Schuster所有,他自己也是前南斯拉夫的移民。走线人就在漏洞边上安营扎寨,砍他的树取暖,等待边管接收。他估计现在每周有3000人通过这个漏洞进入美国。
7. 边管会把走线者带到就近的圣地亚哥看守所,进行背景调查和问询,一般在72小时内,他们会被释放,然后可以填写庇护申请表了。记者问为什么他们会主动被边管找到?官员说这样既安全又有效率,但在这种边境口岸申请庇护有难度,其中就包括不怎么好用的庇护申请APP。
8. 由于两国关系的原因,在2016年美国签发给中国人的签证的数量是220W,到了2022年,这数字变成了16W,缩水了93%。
9. Tammy Lynn是有着20年经验的中国移民律师,她表示即使这些走线者申请庇护被拒了,由于中国不接受遣返,所以他们也不会被遣返,至少她没见过。一共有3.6W中国非法移民被要求离开美国,但由于中国不接收,而美国也不能强迫中国接收,所以这些非法移民会被陷入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去年有55%的中国走线者被给予了庇护,而其他国家平均只有14%。
10. 记者问老Jerry,“你问过边关,你们就不能把这个漏洞堵上吗?”。Jerry回答,是的,他们说“这事情我们管不了,你得打电话给华盛顿。”于是记者就质问了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他们回答道:他们没有权力阻止走线者通过这个漏洞进入美国,只能在他们非法进入后逮捕他们。至于堵上漏洞这个问题,他们回应到: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但需要国会给我们批钱。
最后发下油管下面的高赞评论:
- 在这个国家我们真的很愚蠢(2.8K赞)
- 太疯狂了(1.3K赞)
- 如果老Jerry租了一个超大推土机,把漏洞平了并堵上一块大石头,会发生什么?他会因阻止大量非法移民而被逮捕吗?(400赞)
- 这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260赞)
- 他们能够光明正大地进来真是太疯狂了(500赞)
报道被马一龙转发了

附录罗斯巴德批评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豆瓣用户久道短评:
我们的常识是,亚当·斯密是现代自由市场理论的奠基人,但罗氏以详实的经济史资料证明,此人不但大量抄袭,而且浪得虚名,远不及当时法国的杜尔阁等人。他否定了价值的主观性,将其视为对应了某种劳动时间的客体,这就为李嘉图以及随后马克思等提出“剥削”理论奠定了基础。斯密蔑视消费的主观性,他也无视放债的时间主观性,因此反对民间融资。他的思想,其实有浓厚的加尔文疯子色彩。通过罗氏分析,新教、加尔文最早都是与反动王党、乌托邦主义、重商主义结盟的。
附录《自由平等博爱》批判穆勒
附录【吴钩】“王安石变法”与“罗斯福新政”有什么关系?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赐稿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辛丑十一月十三日戊戌
耶稣2022年1月16日

钱穆曾讲过一件佚事:“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指常平仓制度),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忱。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
钱穆所述确有其事,华莱士访华的时间是1944年,当时媒体亦有报道:“华氏(即华莱士)研究中国历史,对于吾国王安石之农政,备至推崇,迭次言论中皆有向往之词”;在与中方接待人员谈话时,华莱士“亦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关各节,华氏誉王安石为中国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发表演讲时,华莱士又说,“彼(即王安石)于一○六八年在重大困难之下,所遭遇之问题与罗斯福总统在一九三三年所遭遇之问题,虽时代悬殊,几乎完全相同,而其所采方法,亦非常相似”。
按华莱士此说,宋代中国的王安石变法居然与20世纪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产生了联系。
众所周知,上世纪20年代末美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胡佛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应对危机失败,1932年罗斯福击败胡佛,当选美国总统,并于次年开始推行具有明显干预主义色彩的新政,其中的农业新政就是由时任农业部长的华莱士操刀的。华莱士自述:“我任农业部长后,不久就请求国会在美立法中加入中国农政的古法,即‘常平仓’的办法。这个常平仓的名字,我是得自陈焕章所著的《孔子与其学派的经济原则》。”
陈焕章,康有为弟子,光绪三十年进士,随后赴美留学,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出版论著《孔子与其学派的经济原则》(今译《孔门理财学》),1930年再版。陈焕章以现代经济学的概念与语言向西方社会介绍了传统中国的经济学说与与经济制度,其中包括常平仓制度与王安石新法,在西方反响很大,引起了经济学家凯恩斯、熊彼特、社会学家韦伯的注意。华莱士正是通过阅读陈焕章的著作,了解了传统中国的常平仓制度,以及由常平仓制度改良而来的王安石“青苗法”(又称“常平新法”)与“市易法”(又称“常平市易”)。
罗斯福新政期间,华莱士参考常平仓制度、王安石“青苗法”与“市易法”,制订了一系列农业新政,包括:1)农业部成立“商品信贷公司”,向农场主、农民提供以农产品为抵押的贷款;2)设立“联邦剩余商品救济公司”,通过收购过剩农产品再分发给城市贫民的方式稳定农产品市场价;3)联邦剩余商品救济公司还具有常平仓的功能,在丰年收购、储藏五种农产品(玉米、小麦、稻谷、棉花与烟草),以备灾荒,歉年则抛售储备的农产品;4)当“常平仓”的储备过剩时,国家对农产品销售实施配额制。
-195.jpg!article_800_auto)
从罗斯福政府的农业新政,确实可以看到王安石“青苗法”、“市易法”的影子,华莱士称王安石变法与罗斯福新政“所采方法,亦非常相似”,并非虚言。因此,一些研究者坚定地相信,“青苗法和市易法等措施是美国‘常平仓计划’的制度原型。王安石对华莱士的影响线路主要从陈焕章而起,当时有关中国古代思想的大量文献,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变法的青苗法和市易法内容直接影响到他。”
美国人华莱士对王安石变法的重新发现、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经济危机的成功挽救,也许正好印证了陈焕章的一个论断:“对我们而言,《周礼》中的某些法规(即王安石的新法)似乎可以应用于现代民主社会。以政府借贷为例,……如果在各方面都具备优良的管理制度,那么,政府最薄息的借贷不仅帮助了处于困难中的民众,而且,也增加了国家的收入。王安石确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他却生不逢时。”
第1章 市场的力量
每天,我们每一个人为了吃、穿、住,或干脆为了享乐,消耗无数的货物和劳务。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什么时候我们要买这些东西,就能买到。我们从不停下来想一下,有多少人这样那样出了力,提供这些货物和劳务。我们从不问一问自己,为什么街角那个小店——或者现在的超级市场——的货架上总有我们想买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能够挣到钱来购买这些货物。
人们自然可以假设,一定有谁在发号施令,保证以“适当的”数量生产“适当的”产品,投放到“适当的”地方。这是一种协调大批人活动的方法,即军队的方法。在军队里,将军下命令给上校,上校给少校,少校给中尉,中尉给军士,军士再下命令给士兵。
但是,完全靠这种方法或主要靠这种方法,只能指挥一个很小的集团。即使是最专断的家长,也不可能完全靠命令来控制家里其他成员的每一行动。没有哪一支庞大的军队能够真正完全靠命令来统率。将军显然不可能掌握必要的情报来指挥最低级的士兵的每一行动。在指挥系统的每一级,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必须注意考虑特殊情况,即考虑上级不可能了解的情况。指挥必须以自愿的合作来补充——这种合作不那么明显可见,比较难于捉摸,但却是协调大批人活动的最为基本的方法。
……
这种自发的市场因素虽然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抵触,但却获得了很大发展,因为要消灭它们,代价太大。自留地是可以被禁止的,但人们一想起三十年代的饥荒,便感到不寒而栗。现在苏联的经济已很难说是高效率的典范了。要不是有那些自发的因素,它运行的效率肯定还会更低。最近柬埔寨的经验悲剧性地说明,完全不要市场,会使人们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正如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完全按指挥原则运行那样,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完全通过自愿的合作来运行。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些指挥的成分。它们可采取多种形式。可以是直截了当的。如征兵,禁止买卖鸦片或甜味素,法院禁止被告或要求被告采取某些行动;也可以是非常隐蔽的,如征收重税来劝阻人们吸烟——如果这不算命令的话,可以说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一种暗示。
两者如何搀合,关系极为重大。或是自愿的交易基本上是地下活动,其发展是由于占支配地位的指挥成分过于死板;或是自愿的交易成为主要的组织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指挥成分的补充。地下的自愿交易可以防止统制经济崩溃,可以使它艰难地运行,甚至取得某些进展。对于主要以统制经济为基础的专制统治来说,它起不了什么破坏作用。另一方面,自愿交易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内部就具有促进繁荣和人类自由的潜力。它也许在这两方面不能完全发挥其潜力,但就我们所知,凡达到过繁荣和自由的社会,其主要组织形式都必然是自愿交易。不过我们要赶紧补充一句:自愿交易并不是达到繁荣和自由的充足条件。这至少是迄今为止的历史教训。许多以自愿交易为主组织起来的社会并没有达到繁荣或自由,虽然它们在这两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独裁社会大得多。但自愿交易却是繁荣和自由的必要条件。
通过自愿交易进行合作
有一个有趣儿的故事,名叫“小铅笔的家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自愿的交易怎样使千百万人能够互相合作。
价格的作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的主要思想,简单得常常使人发生误解:如果双方的交换是自愿的,那就只有在他们都相信可以从中得益时,才会做成交易。经济上的谬论,大都是由于人们忽视了这个简单的道理,而往往认为,就那么一块饼,一方要多得就必得牺牲另一方。
斯密的这一见解在两个人之间的简单交易中是容易理解的。但要懂得它怎么能使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合作来促进他们各自的利益,就困难多了。
【注:财富是创造出来的,自发交换显然有助于实现帕累托最优!】
亚当·斯密的天才的闪光在于他认识到,在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愿交易中——简单地说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出现的价格能够协调千百万人的活动。人们各自谋求自身利益,却能使每一个人都得益。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秩序可以作为许多各自谋求自身利益的人的行动的非有意识的结果而产生,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思想,直到今天仍不失其意义。
【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第二十》)
价格制度运行得这样好,这样有效,以至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感觉不到它。直到它的运行受到阻滞,我们才认识到它的良好作用,但即使到那时,我们也很少认识到麻烦的根源。
1974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石油禁运之后突然出现的排长队买汽油的现象,和1979年伊朗革命后的春夏两季再度出现的同样现象,是最近这方面的显著例子。这两次石油危机,使原油的进口供应陷入了极度混乱的状态。但这在完全依靠进口石油的日本和西德并没有导致人们排队买汽油。而在自己生产许多石油的美国却导致了排长队,其原因,也是唯一的原因,是由于政府部门执掌的法规不允许价格制度起作用。在一些地区,价格被指令控制得过低,而价格稍高一点本来是可以使加油站有足够的油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的。石油按命令分配给全国各地,而不是按在价格上反映出来的需求的压力,其结果是在一些地方过剩,而在另一些地方是缺货和排长队。价格制度的顺利运行——数十年来它保证了每个消费者能够随自己的便在任何一个加油站不必怎么等待就买到汽油——被一种官僚主义的即兴之作代替了。
价格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起三个作用:第一,传递情报;第二,提供一种刺激,促使人们采用最节省成本的生产方法,把可得到的资源用于最有价值的目的;第三,决定谁可以得到多少产品——即收入的分配。这三个作用是密切关联的。
传递情报(信息)
假设,不管是什么原因,对铅笔的需求有所增加——也许是因为出生的孩子多增加了学生人数。零售商发现铅笔的销路增加了。他们会向批发商定购更多的铅笔。批发商会向制造商定购更多的铅笔。制造商会定购更多的木料、黄铜、石墨——用于制造铅笔的所有各种产品。制造商为了使他们的供应者更多地生产这些产品,就得出更高的价钱。较高的价钱会促使供应者增加他们的劳动力,以便应付增加了的需求。为了得到更多工人,他们就得出较高的工资或较好的工作条件。这样,就象水波似的愈来愈扩大,把消息传给全世界,知道对铅笔的需求增加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对某种他们生产的东西的需求增加了,他们可能知道其原因也可能不知道其原因。
价格制度只传递重要的情报,而且只传递给需要知道的人。举例说,木材商并不需要知道,铅笔的需求增加是因为小孩出生得多还是因为有一万四千份政府公文要用铅笔填写。他们甚至无需知道铅笔的需求增加。他们只需要知道有人愿意为木料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这个价钱会维持很久,值得去满足这种需求。这两种情报都来自市场价格——前一种来自现时价格,后一种来自期货价格。
要有效地传递情报,一个大问题是保证每一个能使用这种情报的人得到它,不让那些不需要它的人把它束之高阁。价格制度自动解决了这个问题。传递情报的人受到一种刺激,去寻找能使用情报的人,而且他们最后是能够找到的。能够使用情报的人也受到一种刺激去获得情报,而他们最后也是能够得到情报的。铅笔制造商同卖给他木料的人接触。他总是试图找到新的供应者,能够提供较好的产品或是要较低的价钱。同样,木材商人同他的顾主接触,并总是试图找到新的顾主。另一方面,那些眼下不从事这些活动而且将来也不打算从事这些活动的人,则对木料的价格不感兴趣而予以漠视。
【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只能缓解,而不能消除!】
通过价格传递情报,当今由于有组织良好的市场和专业化的消息传送设施,而大为方便了。看一看《华尔街日报》上每天的行情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且不说许多更专业化的商业出版物。这些价格几乎是当即反映全世界发生的事情。在遥远的一个主要产铜国家发生了革命,或是由于其他原因,铜的生产中断,铜的现价会立刻陡涨。要了解熟悉行情的人估计铜的供应会受多久的影响,你只需要查一下同一版上的期货行情就行了。
即使是《华尔街日报》的读者,大多也只关心少数几种价格。他们可以不管其他的价格。《华尔街日报》提供这种情报,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也不是因为它认识到这个经济的运行是何等重要。促使它提供情报的,就是那个它促进其运行的价格制度。它发现,公布这些价格——即另一套价格传递给它的情报——能增加报纸发行量从而赚更多的钱。
价格不仅把情报从最终的购买者那里传给零售商、批发商、制造商和拥有各种资源的人,它们还以其他方式传递情报。假定有一处森林失火或是工人罢工,使木材供应减少而木材的价格上涨,这就告诉铅笔制造商应该少用木料。如果还生产原先那么多铅笔而又不能加价售出,那就要吃亏。铅笔的产量缩减,会使零售商提高价格,而加价会使使用者把铅笔用得更短或者改用自动铅笔。使用者用不着知道铅笔为什么涨价,而只需知道铅笔涨价就行了。
阻止价格自由地反映供求状况,会妨碍情报的精确传递。私人垄断——由一个生产者或生产者卡特尔操纵一种特定的商品——就是一个例子。这并不妨碍通过价格制度传递情报,但它的确歪曲所传达的情报。1973年石油卡特尔把油价提高三倍,传递了很重要的情报。但是这个价格所传递的情报并不反映石油供应的突然减少,也不反映关系到未来石油供应的新技术知识的突然发现,或是别的什么能够确实影响石油和其他能源供应的事情。它只是传递了这样一个情报:一些国家成功地达成了定价和分销协议。
美国政府对石油和其他能源实行价格管制,妨碍了价格把石油卡特尔的影响精确地传送给用油者。其结果是,由于不让价格的上涨来促使美国消费者节约石油而加强了石油卡特尔的地位,同时迫使美国建立庞大的控制机构,来分配不足的供应(一个能源部1979年开支约一百亿美元,雇用了两万人)。
私人对于价格的歪曲固然重要,但在当今,政府是对自由市场制度的主要干扰源。干扰的方法是征收关税和对国际贸易实行其他限制,采取冻结或影响价格(包括工资)的国内措施(见第二章),管理某些行业(见第七章),以及采取货币和财政政策来造成反常的通货膨胀(见第九章)。
反常的通货膨胀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之一,可以说是使价格传递情报的作用失灵。例如,如果木材的价格上涨,木材制造商无法知道这是因为通货膨胀使物价普遍上涨呢,还是因为在涨价前木材同其他产品相比,需求有所增加而供应有所减少。对于组织生产来说,重要的是关于比较价格即一种东西和其他东西相比的价格的情报。高度的通货膨胀,特别是变化无常的通货膨胀使这种情报陷于无意义的静态。
刺激(激励)
精确情报的有效传递,如果不能刺激有关的人去根据这种情报采取适当的行动,那传递情报就毫无意义。如果有人告诉木材生产者市场对木材的需求有所增加,但这并没有刺激木材生产者生产更多的木材来对涨价作出反应,那就没有必要告诉他这件事。自由价格制度的妙处之一是,传递情报的价格也提供刺激,使人对情报作出反应,还提供这样做的手段。
价格的这个作用同第三个作用——决定收入的分配——密切关联,不把后者考虑在内就说不清楚。生产者的收入——他的活动所得——取决于他出售产品的所得和制造产品的开销之间的差额。他反复权衡二者,最后确定的产量使他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再多生产一点会使增加的成本同增加的收入相等。而价格的提高改变了这种状态。
【注: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即边际利润=0】
一般说来,他生产得越多,生产的成本也越高。他必须采伐更偏僻或其他条件更差的地方的树木;他必须雇用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人,或者付出较高的工资以从其他行业吸引熟练工人。但是现在价格提高了,使他能够承受较高的成本,这就提供了增加生产的刺激和这样做的手段。
价格还提供另外一种刺激,使人不仅按关于需求增加的情报行动,还按关于最有效的生产方法的情报行动。假定有一种木材因短缺,而比别的木材贵,铅笔制造商便获得这种木材涨价的情报。由于他的收入也取决于售货所得和制造成本之间的差额,他就受到一种刺激去节省那种木材。换一个例子,伐木工人使用链锯还是手锯,那要看链锯和手锯的价格,哪一种成本低,要看每种锯需要的劳动量以及不同种劳动的工资。因而伐木行业受到一种刺激去获得有关的技术知识,并把它同价格所传递的情报结合起来,以最大限度降低成本。
还可以举另一个更为有趣的例子来说明价格制度的微妙作用。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石油的价格,增加了使用链锯的成本,使情况变得稍稍对手锯有利。如果这个例子似乎太牵强,不妨想一想石油涨价对运送木材的两种卡车的影响,一种是烧柴油的,另一种是烧汽油的。
把这例子推进一步,石油的涨价,就其容许发生的程度来说,增加了用油多的产品的成本,增加的幅度要大于用油少的产品的成本。因而消费者受到一种刺激而改用后一种产品。最明显的例子是人们从前喜欢体积大的汽车,现在喜欢体积小的汽车,从前用石油取暖现在改用煤炭或木柴取暖。让我们进一步来看更深远的影响:生产成本的增加或需求量的增加(由于把木头作为替代能源),使木材的比较价格上涨,由此引起的铅笔的涨价,这给消费者一种刺激,使之节约铅笔;凡此种种,价格的变化会带来无穷的影响。
迄今我们只论述了价格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刺激作用,实际上它对其他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和工人也起作用。木材需求量的增加会使伐木工人的工资提高。这是一种信号,表明对那种劳动的需求增加了。工资的提高刺激了人们,使一些原来不想当伐木工人或干其他活儿的人现在愿意当伐木工人了。进入劳动市场的年青人更多地成为伐木工人。在这里,政府和工会的干预同样会歪曲所传递的情报或阻碍个人根据情报而自由行动,前者的干预手法是规定最低工资,后者的干预手法是限制人们进入这个行业(见第八章)。
关于价格的情报——不论是各行各业的工资或地租,还是资本用于各种用途带来的收益——并不是唯一关系到决定如何使用某一种资源的情报。它甚至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情报,特别是当关系到如何使用自己的劳动的时候。最后的决定除价格外,还取决于个人的兴趣和本事——即取决于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称之为一种职业的、货币的或非货币的全部有利之处和不利之处。对一种职业感到满意可以补偿较低的工资。另一方面,较高的工资可以补偿不惬意的工作。
收入的分配
我们知道,一个通过市场获得收入的人,他的收入取决于他出售货物和劳务的所得同他在生产这些货物和劳务时所花费的成本之间的差额。所得主要是直接付给我们拥有的生产资源的款项——如付给劳动的工资或付给土地建筑物或其他资本的使用费。企业家——如铅笔制造商——的情况形式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他的收入也取决于他拥有的每一种生产资源的多寡,取决于市场为使用这些资源确定的价格。不过企业家拥有的生产资源主要是组织企业,协调企业资源以及承担风险等方面的能力。他也可以拥有一些企业所使用的生产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收入,部分就取自使用这些资源的市场价格。同样,现代公司的存在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我们泛泛地说到“公司收入”或有收入的“企业”。这是比喻的说法。实际上,公司是业主即股东和除股东资本(公司所购买的这种资本的劳务)外的资源这二者之间的媒介。只有人才得到收入,他们通过市场,从他们拥有的资源上面得到收入,不管这些资源采取什么形式,是公司股票、债券、土地还是他们个人的能力。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主要的生产资源是个人的生产能力,即经济学家的所谓“人力资本”。美国通过市场交易产生的总收入中,大约有四分之三是雇员的报酬(工资、薪金以及补助),其余部分约有一半是农场主和非农业企业主的收入,这里面既有对个人劳务的报酬又有使用企业主资本的费用。
物质资本——工厂、矿山、办公楼、商店;公路、铁路、机场、汽车、卡车、飞机、船只;水坝、炼油厂、电站;住房、冰箱、洗衣机,等等——的积累对经济增长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物质资本的积累,我们决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经济发展。不维持代代传下来的资本,一代的所得就会被下一代花光。
但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其形式是知识技能的提高、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寿命的延长——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相辅相成的。物质资本为人提供工具,使他大大提高生产力。而人能够发明新形式的物质资本,懂得使用物质资本,从中得到最大好处,并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组织使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使物质资本更富于生产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必须得到照管和替换。人力资本要比物质资本更难于照管和替换,而且照管和替换的费用更大——这就是为什么人力资本得到的报酬要比物质资本得到的报酬增长得快得多的主要原因。
我们每一个人拥有的每一种资源的数量,部分取决于偶然性,部分取决于我们自己或别人的选择。偶然性决定我们的基因,基因影响我们的体格和智力。偶然性决定我们的出身和文化环境,从而决定我们发展自己体力和脑力的机会。偶然性还决定我们可能从父母或其他施舍人那里继承的资源。偶然性可能破坏或增加我们最初的资源。但是选择也起重要的作用。我们决定怎样使用我们的资源,是勤奋工作还是随随便便,是干这一行或是另一行,是从事这种冒险还是另一种冒险,是积蓄还是花费——这些可以决定我们是消耗资源还是改善和增加资源。我们的父母、其他施舍人以及千百万可能同我们毫无关系的人的同样决定也会影响我们继承的东西。
市场为使用我们的资源规定的价格,也受偶然性和选择的影响。弗兰克·西纳特拉的嗓子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备受欢迎。要是他碰巧出生和生活在印度,是否也能受到欢迎呢?狩猎的技能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美国用处很大,而在二十世纪的美国用处就小得多了。棒球手的技术在二十年代要比篮球运动员的技术得到高得多的报酬,但在七十年代却正好相反。所有这些事情都牵涉到偶然性和选择——就这些例子来说,大多是劳务消费者的选择决定不同项目的相对市场价格。但是我们通过市场从资源的劳务上面所得到的价格也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在哪儿定居,怎样使用我们的资源,把资源的劳务出售给谁,等等。
在任何社会里,不管它是怎样组织的,总有对收入分配的不满。我们大家都感到难以理解,我们的收入为什么少于那些看来并不比我们强的人,或者,我们的收入为什么多于大多数人,他们不是也很需要,哪一方面也不比我们差吗?远处的田野总是显得更绿——于是我们就归咎于现存的制度。在统制制度下,妒嫉和不满针对统治者。在自由市场制度下,就针对市场。
结果之一是人们试图把价格制度的这种作用——分配收入——同它的其他作用——传递情报和提供刺激分开来。在美国和其他主要依赖市场的国家,近几十年的政府活动有许多就是为了改变收入分配受市场支配这种状况的,以便用另一种更为平均的方式分配收入。目前公众舆论的压力很大,要求在这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我们将在第五章里较为详尽地讨论这一问题。
如果我们不利用价格来影响收入分配,且不说完全决定收入分配,那么,不管我们的愿望如何,要利用价格来传递情报,刺激人们行动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个人的所得如果不取决于其资源提供的劳务应得到的价格,那什么会刺激他寻找有关价格的情报或根据这个情报采取行动呢?如果不管雷德·阿德尔干不干堵塞失去控制的油井这种危险工作,他的收入都一样,那他为什么要干这样危险的工作呢?他可能因一时冲动干一会儿。但是他会以此为职业吗?如果不管努力工作与否,你的收入都一样,那你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呢?如果你费了很大劲儿找到了愿意出最高的价钱购买你要出卖的东西的买主,但实际上却得不到任何好处,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如果积累资本得不到报酬,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把现在可以享受的东西推迟到将来享受呢?为什么要积蓄呢?人们的自愿节制怎么会积累现在这么多物质资本呢?如果维持资本得不到报酬,那么人们为什么不把积累或继承的资本消耗掉呢?由此可见,如果人们不让价格影响收入的分配,他们也不能利用价格干别的事情。唯一的替代办法是实行控制。由某个政府机构来决定谁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某个政府机构来决定谁该扫街,谁该管理工厂,谁该当警察,谁该当医生。
在共产党国家,价格制度的这三种作用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的。这些国家思想意识的基础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遭受着所谓剥削,而按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一马克思的名言建立的社会则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但是,由于纯粹的统制经济是无法运转的,它们不可能把收入完全同价格分开。
对于物质资源——土地、建筑物等等——共产党国家采取了极端措施,把它们变成了政府的财产。其后果是减少了维持和改善物质资本的刺激。大家都拥有某种东西而又没有一个人拥有它,维持或改善物质资本的状况同任何人都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的建筑物——象美国的公共房屋那样——才建起一两年就显得破旧,为什么国营工厂的机器经常出故障,需要修理,为什么公民不得不求助黑市来维持他们个人使用的资本的缘故。
对于人力资源,共产党政府没有能够走得象处理物质资本那么远,虽然它们曾经尝试过。它们不得不容许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自己的命运,让他们作出自己的决定,不得不让价格来影响和指导这些决定并规定收入的分配。当然,它们歪曲了价格,不让它成为自由市场价格,但它们终究没能取消市场力量。
统制经济效率的明显低下,使社会主义国家——俄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中国——的计划人员不得不认真考虑在组织生产时更多地利用市场的可能性。在一次东西方经济学家的会议上,我们有一次听到匈牙利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侃侃而谈,声称重新发现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成就,如果不是有点多余的话。他试图改造这只手,想利用价格制度来传递情报和有效地组织生产,但不让它分配收入。不用说,他在理论上失败了,正如共产党国家在实践上遭到了失败一样。
【注:最新版本中这里删改挺严重。】
更广泛的见解
人们一般认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只对货物或劳务的买卖起作用。但经济活动并不是人类活动的唯一领域,在其他领域里,也同样是在每个人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同其他人合作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了错综复杂的结构。
让我们以语言为例。语言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结构,但却秩序井然,丝毫不乱,这并非有任何中央机关在计划它。没有人决定什么词该用到语言里,文法应该是什么样,哪些词应该是形容词,哪些词应该是名词。法兰西学院倒是试图控制法国语言的变化。但为时已晚。它建立时,法语早已成了结构精巧的语言,它只不过是批准已经发生的变化而已。其他国家还很少设立这样的机构来控制语言。
语言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语言的发展同经济秩序通过市场而发展的过程很相象,也是由于个人之间自愿的相互作用造成的,不过在这里相互谋求交换的是思想、情报或传闻,而不是货物和劳务。人们赋予一个词这样或那样的意义,或者当需要的时候创造新词。人们越来越多地按某种顺序运用语言,后来就形成了规则。愿意相互交流思想的双方对他们所使用的词规定相同的意思,由此而得到了便利。当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时,一种共同的用法就传开来,这个词也就被收入了字典。在这里,没有任何强制,没有中央计划人员发号施令。不过近来公立学校在使字词的用法标准化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个例子是科学知识。各学科的结构—一物理学、化学、气象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并不是任何人深思熟虑的产物。它象托普西(译注:小说中一孤儿名,她毫不费劲地成长)那样,“只管一个劲儿地成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者们感到这样方便。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各种需要的发展而变化的。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与经济市场的发展极其相似。学者们相互合作,因为他们发现这样做相互有利。他们从相互的工作中接受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他们通过交谈、传阅未出版的材料、出版杂志或书籍等方式交换研究成果,合作是世界范围的,就象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学者同行们的尊敬和赞同所起的作用,同货币报酬在经济市场上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为了博得人们的尊敬,让同行接受他们的成果,学者们往往在最有科学价值的方面下功夫。一个学者在另一学者的成果上发展,使总体比单个加在一起的总和更大。他的成果反过来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正如现代的汽车是货物自由市场的产物一样,现代物理学是思想自由市场的产物。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科学知识的发展也受到了政府干预的许多影响,这种干预影响了资源的利用和社会需要的知识的发展。不过到目前为止,政府的影响还不是特别严重的。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曾经强烈赞成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中央计划的学者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由政府对科学进行中央计划会给科学的发展带来多么大的危险。他们担心各门学科的先后发展顺序将由上面来确定,而不是通过科学家的探求和摸索自然而然地形成。
一个社会的价值准则、它的文化、它的社会习俗,所有这些都是通过自愿的交换和自发的合作发展起来的,其复杂的结构是在接受新东西和抛弃旧东西、反复试验和摸索的过程中不断演变的。举例来说,没有哪一个君王规定过,加尔各答居民欣赏的音乐应该根本不同于维也纳居民欣赏的音乐。各国大不相同的音乐史,没有经过任何人的“规划”,而是通过一种与生物进化相平行的社会进化发展起来的。当然,个别的君主以至民选的政府可以象大富翁那样,倡导某种音乐或资助某个音乐家,从而影响音乐的自然发展。
自愿的交换产生的结构,不论是语言、科学发明、音乐风格还是经济制度,都有其自己的生命。它们能够在不同情况下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自愿的交换能够在某些方面产生一致而又在其他方面产生不同。这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过程,它的总的运行规律不难掌握,但它所产生的具体结果却很少能被人们预见到。
上述例子不仅说明了自愿交换发生作用的巨大范围,而且还说明必须给予“私利”这个概念以广泛含义。狭隘地专注于经济市场,导致了人们狭隘地解释私利,说私利就是目光短浅的自私自利,只关心直接的物质报酬。经济学受到斥责,说它只是依靠与现实完全脱节的“经济人”来得出一般性经济结论,而这个“经济人”不过是一架计算机,只对金钱的刺激作出反应。这是巨大的误解。私利不是目光短浅的自私自利。只要是参与者所关心的、所珍视的、所追求的,就都是私利。科学家设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传教士设法把非教徒变成教徒,慈善家设法救济穷人,都是在根据自己的看法,按照他们认定的价值追求自己的利益。
政府的作用
政府是怎么牵扯进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政府是自愿合作的一种形式,是人们挑选来达到某些目标的方法,因为他们相信,政府是实现某些目标的最有效的方法。
最明白的例子是,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在哪里,也就是说可以自由选择受什么样的地方政府的统治。你决定住在这个地方而不住另一个地方,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务不同。如果它从事的活动你反对或不愿为之出钱,它们不是你赞成和愿意为之出钱的活动,那你可以迁到别处去。只要有选择,就有竞争,尽管竞争往往是有限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
然而,政府并不仅仅是一种选择。它还是一个机构,广泛地被认为拥有独断的权力,可以合法地使用强力或以强力为威胁,来使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得以合法地强制另一些人。政府的这一更为基本的作用,在大多数社会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在任一特定时期里,政府的这一作用在各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别。本书的其余部分将用许多篇幅来论述最近几十年中美国政府的作用是怎样变化的和它的活动产生了什么影响。
在开始简要地论述这一问题的时候,让我们先考虑一个看起来很不相关的问题。假设有这样一个社会,其成员希望作为个人、家庭、自愿集团的成员或有组织的政府的公民,获得尽可能多的选择自由,那政府应该起什么作用呢,亚当·斯密在二百年前最为圆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任务虽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
前两项义务是简单明了的:必须保护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免遭外国人或自己同胞的强制。没有这种保护,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选择自由。手执凶器的强盗在抢劫的时候常说,“你要钱还是要命?”这也是一种选择,但谁也不会说这是自由的选择,说受害者的交换是自愿的。
当然,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反复看到的那样,一个机构尤其是政府机构“应该”实现的目标是一回事,而这个机构实际实现的目标则是另一回事。负责建立某一机构的人的意图,同管理这个机构的人的意图往往大不相同。同样重要的是,所取得的结果常常同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大不一样。
【注:这和程序一样,代码是按照写的方式执行,而不是按照想的方式执行。】
防止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强制,需要有军队和警察。但军队和警察并不总是成功的,它们有时把权力用于同自己的职能很不相干的目的。要建成并维护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确保赋予政府的强制力量只用于维护自由,而不变成对自由的威胁。我国的创建人在起草宪法时曾为此煞费苦心,但我们却往往忽视这一点。
亚当·斯密提出的第二项义务,不仅包括警察职权范围内的事,即保护人们不受肉体的强制,而且还包括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自愿的交易,只要是复杂的或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难免有含混的地方。世界上还没有那么好的印刷品,能事先写明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事件,确切说明交易各方在每一场合下的义务,因而总得有某种方法来调解纠纷。这种调解本身可以是自愿的,无须政府插手。在今天的美国,商业合同方面的纠纷,大多靠事先选好的私人调解人来解决。为适应这一需要,产生了一个庞大的私人司法体系。但是,最后的裁决,往往仍然要由政府的司法机关来作出。
政府的这个作用还包括制定一般性规则,也就是制定自由社会的公民在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时应遵守的规则,以便利自愿的交易。最明显的例子是私有财产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我拥有一所房子。如果你驾驶私人飞机在我屋顶上方十英尺的空中飞过,这算不算“侵犯”了我的私有财产?如果是在一千英尺或三千英尺的空中飞过呢?我的产权止于什么地方,你的产权始于什么地方,并没有“自然的”规定。社会主要是靠习惯法来规定产权的含义,虽然近来立法所起的作用不断增加。
亚当·斯密提出的第三项义务,是人们最争论不休的问题。他本人认为这项义务适用的范围很窄。但有些人却一直用它来为政府开展极为广泛的活动作辩护。依我们看,斯密提出的第三项义务是政府应当肩负的一项正当义务,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加强自由社会;但政府也可以以此为理由,无限扩大自己的权力。
其所以正当,是因为通过严格自愿的交易生产某些货物和劳务花费太大。让我们来看斯密在说明第三项义务时所举的一个简单例子:城市的街道和公路可以通过私人的自愿交易来建造,费用靠征税偿付。但征税的开支同建造并维修这些街道或公路的花费相比,往往过于庞大。所谓“公共工程”,是指那些不是“为了任何个人的利益而建立和维持的工程……但它们”却值得“大社会”来建立和维持。
一个更不易捉摸的例子涉及对“第三者”的影响。“第三者”是指某一交易以外的人。这个例子说的是“烟尘的污害”。你的炉子喷出烟尘,弄脏了第三者的衣领。你无意中让第三者付出了代价。如果你愿意赔偿,他也许乐意让你弄脏他的衣领——但是要找出所有受到影响的人,或者这些人要找出谁弄脏了他们的衣领,要求你各个赔偿损失或者同他们各个达成协议,是根本办不到的。
【注:外部性
你加给第三者的影响也可能并不需他们付出代价,反倒给他们带来好处。你把房屋周围绿化得很美,使所有过往行人都享受到这景色。他们可能愿意为得到这样的特权偿付点什么,但是要他们为观看你可爱的花草而缴钱,是行不通的。
用行话来说,“外界的”或“邻居的”影响会使“市场失灵”,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让受到影响的人得到补偿或付出代价,因为这样做费用太大;第三者被强加了不自愿的交易。
我们做任何事情,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会对第三者产生一些影响,不论这种影响是多么微小,或受到影响的人距离我们多么遥远。结果,乍看起来,似乎政府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正当的,都是亚当·斯密的第三项义务所允许的。但这纯粹是误解。政府的措施也会对第三者产生影响。“外界的”或“邻居的”影响不仅可以使“市场失灵”,而且也可以使“政府失灵”。如果这种影响对于市场交易是重要的话,那它对于政府采取的旨在纠正“市场失灵”的措施多半也是重要的。私人活动对第三者的影响之所以意义重大,主要是因为难以弄清给外界带来的损失或好处。在容易弄清谁受到损失、谁得到好处而且损失、好处各有多大时,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用自愿交易代替不自愿交易,或者至少是要求得到补偿。如果你的车子撞了别人的车子,责任在你一边,那政府可以迫使你赔偿对方的损失,即使这种交易是不自愿的。如果能很容易地弄清谁的衣领将被弄脏,那你就可以赔偿将要受到影响的人,或者反过来,他们可以付钱给你,好使你的烟囱少冒些烟。
如果私人方面要弄清谁给了谁损害或好处,是困难的,那么要政府做到这一点也是困难的。因此,政府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最后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把损失加到无辜的第三者头上或者让侥幸的旁观者得到好处。为了开展活动,政府必须抽税,这本身就影响纳税人的作为——这是对第三者的另一种影响。此外,政府权力的每一次扩大,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都会增加这样一种危险,即政府不是为其大多数公民服务,而是变成一些公民压迫另一些公民的手段。可以这样说,每一项政府措施都背着一个大烟囱。
自愿安排接受第三者影响的能力,比我们骤看到时所想象的大得多。举个小例子,在饭馆里面付小费是一种社会习俗,可以使你为你并不认识或不曾见过的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反过来,也使你从另一些不知其尊姓大名的人那里得到较好的服务。不过,私人行动的确对第三者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因而政府有足够的理由采取行动。我们应当从滥用斯密的第三项义务所带来的恶果中吸取教训,但教训不是政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进行干预,而是主张干预的人要肩负严格把关的责任。我们应当对提议中的政府干预详加考察,权衡得失,再行定夺。这样做,不仅因为政府干预的看不见的代价难以估计,而且还出于其他一些考虑。经验证明,政府一旦从事某项活动,就很难停止这项活动。那项活动可能并没有带来预想的结果,但却可能不断扩大,其预算不是被削减或取消,反而是不断增加。
政府的第四项义务,是保护那些被认为不能“负责的”社会成员。亚当·斯密没有明确提到这一义务。象亚当·斯密提出的第三项义务一样,这项义务也很容易被滥用。但这是不容推卸的义务。
自由只是对于负责的个人具有实在意义。我们不相信疯子或孩子的自由。我们必须设法在负责的个人和其他人之间划一界线,但这样做却会使我们最终维护自由的目标变得极为模糊不清。我们不能断然拒绝照管那些我们认为不负责的人们。
【注:打击巨婴,人人有责!】
对于小孩子们,我们把责任首先交给他们的父母。家庭,而非个人,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组成我们社会的基本单位,虽然它已明显削弱——政府干预活动增加的一个最不幸的后果。然而,把管孩子的责任交给父母大多是权宜之计而不是一条原则。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父母比别人更关心他们的孩子,可以信赖他们会保护孩子,并保证他们成长为能负起责任来的人。但我们认为父母无权对孩子为所欲为——打他们、杀他们或者把他们卖给别人当奴隶。孩子生来就是负责的人。他们有他们的基本权利,而不只是双亲的玩物。
亚当·斯密提出的三项义务,或我们提出的四项义务,确实是“很重要的”,但它们远不象斯密所想象的那样“易于为一般人所理解”。虽然我们不能机械地根据这些义务来确定政府已经进行或打算进行的每一项干预活动是否可取,但它们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原则,可以用来权衡利弊。即使作最自由的解释,它们也屏除大部分现有的政府干预,即所有那些“不是优惠就是限制的制度”。亚当·斯密曾坚决反对这些制度,而且最后摧毁了它们,但后来它们又以如下各种方式重新出现了:关税、政府对物价和工资的管制、对从事各种职业的限制、以及其他许多背离了斯密的“简单的自然自由制度”的干预。(其中许多将在以下各章里讨论。)
实践中的有限的政府
在当今世界上,似乎到处都是庞大的政府。人们也许要问,当今是否有这样的社会:它们主要依靠自愿交易,通过市场组织它们的经济活动,其政府只限于履行我们提出的四项义务。
也许最好的例子是香港。这是与大陆中国相邻的一块芝麻粒大小的地方,面积不到四百平方英里,却拥有差不多四百五十万人口。人口的密度几乎是不可置信的,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十四倍于日本,一百八十五倍于美国。然而,香港人却享有全亚洲最高的生活水平,仅次于日本也许还有新加坡。 香港没有关税或其他对国际贸易的限制(除了美国和其他一些大国施加的一些“自愿”限制外)。那里不存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指导,没有最低工资条例,没有固定价格。居民自由自在,想向谁买就向谁买,想把东西卖给谁就卖给谁,想怎么投资就怎么投资,想雇什么人就雇什么人,想给什么人干活就给什么人干活。
政府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主要是履行我们上面所说的四项义务,而且它对这四项义务进行非常狭义的解释。它实施法律,维持秩序,提供制定行为准则的手段,裁决争端,方便交通运输,以及监督货币的发行。它为从中国去的难民提供公共住房。虽然香港政府的开支随着经济的增长也有所增加,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属于世界最低之列。因而,低税保持了刺激。工商业者既可以因成功而获利,又必须为失败付出代价。
具有几分讽刺意味的是,英国的一块直辖殖民地香港,竟然成了现代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范例。管理这块殖民地的英国官员之所以能使香港兴旺发达,是因为他们采取的政策与其母国采取的福利国家政策根本不同。
虽然香港是当代的一个杰出范例,但它并不是实践中的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社会的最重要的例子。这样的例子,我们得回到十九世纪去找。一个例子是1867年明治维新后最初三十年的日本,这我们留到第二章去说。
另外两个例子是英国和美国。在为结束政府对工商业的限制展开的斗争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对这种限制的最早的打击之一。这场斗争经过七十年,最后在1846年以取消所谓“谷物法”获胜,该法律对进口小麦和其他粮食(统称谷物)征收关税并施加其他限制。这样开始了历时四分之三世纪的完全自由的贸易,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并完成了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开始的向高度有限政府的过渡。用上面引用的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这个变化使每个英国居民享有了“完全的自由,可以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经济因此而迅速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就更显出了某些贫苦地区的惨景,对此狄更斯和当时的其他小说家都有极其生动的描述。人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英国在世界各地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增加。在上面所有一切获得发展的同时,政府开支却缩减到只占国民收入的很小一部分,从十九世纪初期的接近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降到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统治六十周年大庆时的大约十分之一,这一年可以说是英国鼎盛时期的顶峰。
美国是另一个惊人的例子。十九世纪的美国是征收关税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的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曾为之进行辩护,试图——肯定没有成功——反驳亚当·斯密主张自由贸易的论点。但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那时的关税是很低的,而且政府对国内外自由贸易没有施加多少别的限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移民入境仍然几乎是完全自由的(只是对从东方来的移民施加限制)。正如自由女神铜像上的铭文所说的那样:
给我,你们那疲劳的,你们那穷苦的,你们那挤作一团、渴望自由的人们,你们那富饶的海岸抛弃的可怜垃圾。送给我这些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我在这金门旁举灯相迎。
移民成百万到来,我们成百万地接受。他们不受任何人的干涉,自由自在地生活劳动,日子越过越好。
有些人毫无根据地把十九世纪的美国描绘成剥削成性的资本家和极端个人主义横行的时代。据说,当时垄断资本家残酷地剥削穷人,他们鼓励移民,然后敲骨吸髓地榨取他们的血汗。华尔街被描绘成了欺骗小城镇居民的恶魔,说它专门吸吮中西部农民的血,幸亏他们身体强壮,尽管受尽折磨,还是活下来了。
实际远非如此。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最初来的可能受骗,但十年二十年后仍有成百万人继续到美国来受剥削,就是不可想象的事了。他们来是因为那些先来的人大都实现了自己的希望。纽约的街道不是黄金铺成的,但是苦干、节俭和冒险精神带来了在欧洲不可想象的报酬。新来的移民从东往西扩展。随着他们的扩展,出现了一座座城市,越来越多的土地得到耕种。国家越来越兴旺发达,移民分享了繁荣。
如果农民受到剥削,他们的人数怎么会增加呢,农产品的价格确实下跌了。但这是成功的标志而不是失败的标志,它反映了机器的发展、耕种面积的扩大和交通的改善,所有这一切使农业产量急速增长。最后的证明是农田的价格不断上涨——难道可以说这是农业不景气的迹象吗?
据说,铁路大王威廉·H·范德比尔特在回答记者问时曾说:“公众真该死”。这句话后来竟成了人们指责资本家残酷无情的口实,但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正是在十九世纪,美国的慈善事业获得了蓬勃发展。私人资助的学校成倍增加;对外国的传教活动急剧扩大,非赢利的私人医院、孤儿院和其他许多慈善机构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差不多每一种慈善机构或公共服务组织,从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到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从印第安人权利协会到救世军,都是在那个时期产生的。自愿的合作,在组织慈善活动方面的效率,一点也不比在组织生产谋取利润方面的效率差。
除慈善活动外,文化事业也获得了巨大发展,不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边疆小镇,都修建了美术馆、歌剧院、博物馆以及公共图书馆,而且成立了交响乐团。
政府开支的数额是衡量政府作用的尺度。除了在几次大的战争期间外,政府的开支从1800年到1929年一直没有超过国民收入的约12%。其中三分之二是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大都用于资助教育事业和修建道路。1928年,联邦政府的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约3%。
美国的成功常常被归因于资源丰富和幅员辽阔。这些自然起了作用——但如果这些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又如何解释十九世纪的英国和日本或二十世纪的香港呢?
常有人坚持说,十九世纪的美国人烟稀少,所以政府可以限制自己的活动,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但在人口集中的现代工业社会里,政府必须起大得多的、确确实实的主导作用。这些人如果在香港呆上一小时,肯定会放弃这种看法。
我们的社会是我们自己建立的。我们可以改变各种制度。物质的和人的特性限制了我们选择的余地。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这些都阻止不了我们去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它主要依靠自愿的合作来组织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它维护并扩大人类的自由,把政府活动限制在应有的范围内,使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让它变成我们的主人。
【注:事在人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本节内容概述
自愿交易并不是达到繁荣和自由的充足条件。这至少是迄今为止的历史教训。许多以自愿交易为主组织起来的社会并没有达到繁荣或自由,虽然它们在这两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独裁社会大得多。但自愿交易却是繁荣和自由的必要条件。
价格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起三个作用:第一,传递情报;第二,提供一种刺激,促使人们采用最节省成本的生产方法,把可得到的资源用于最有价值的目的;第三,决定谁可以得到多少产品——即收入的分配。这三个作用是密切关联的。
亚当·斯密: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任务虽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
政府的这个作用还包括制定一般性规则,也就是制定自由社会的公民在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时应遵守的规则,以便利自愿的交易。
政府的第四项义务,是保护那些被认为不能“负责的”社会成员。
现代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范例----香港没有关税或其他对国际贸易的限制(除了美国和其他一些大国施加的一些“自愿”限制外)。那里不存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指导,没有最低工资条例,没有固定价格。居民自由自在,想向谁买就向谁买,想把东西卖给谁就卖给谁,想怎么投资就怎么投资,想雇什么人就雇什么人,想给什么人干活就给什么人干活。
政府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主要是履行我们上面所说的四项义务,而且它对这四项义务 进行非常狭义的解释。它实施法律,维持秩序,提供制定行为准则的手段,裁决争端,方便 交通运输,以及监督货币的发行。它为从中国去的难民提供公共住房。虽然香港政府的开支 随着经济的增长也有所增加,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属于世界最低之列。因而,低 税保持了刺激。工商业者既可以因成功而获利,又必须为失败付出代价。
我们的社会是我们自己建立的。我们可以改变各种制度。物质的和人的特性限制了我们选择的余地。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这些都阻止不了我们去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它主要依靠自愿的合作来组织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它维护并扩大人类的自由,把政府活动限制在应有的范围内,使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让它变成我们的主人。
附录:柬埔寨大屠杀
本文中提到的「最近柬埔寨的经验悲剧性地说明,完全不要市场,会使人们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的背景就是红色高棉上台实行一系列激进的共产主义制度。
红色高棉大屠杀(高棉语:ហាយនភាពខ្មែរ / ការប្រល័យពូជសាសន៍ខ្មែរ,罗马化:Hayonphap Khmer / Karbraly Pouchsasa Khmer),或称红色高棉种族灭绝、赤柬大屠杀、柬埔寨大屠杀或柬埔寨种族灭绝(法语:Génocide cambodgien;英语:Cambodian genocide),亦被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官方称作波尔布特种族灭绝制度[1][2](越南语:Chế độ diệt chủng Pol Pot),是指1975年至1979年初,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共产主义政权在柬埔寨进行的大规模杀戮事件。据各方估计,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柬埔寨全国范围内共有150万至300万人非正常死亡,约占当时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一直以来,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本人的大力支持和援助,同时受到了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斯大林主义等的较大影响。据学者统计,中国的援助占红色高棉总外援的至少90%,仅在1975年,中方就向红色高棉提供了至少10亿美元的无息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2000万美元的“礼物”。1975年4月,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取得实权后,开始激进推行共产主义,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接见了波尔布特,而1976年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等人还亲自访问柬埔寨进行了“指导”并表示肯定。红色高棉试图创建一个农业社会主义的社会,故强迫城市人口全部迁移到乡下,并效仿中国实行“大跃进(Maha lout ploh)”,导致大量人死于疾病、过度劳动或营养不良。同时,波尔布特等人宣称要“洗净平民”,因而开始杀戮;自1976年起,波尔布特又认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于是开始了对柬埔寨共产党内部人员的大清洗,中央高层领导以及军队总参谋部几乎被屠杀殆尽,1978年仅在柬埔寨东部地区就有十万干部和军人被杀。法国学者让·拉库尔特发明“自我屠杀”一词来形容红色高棉。
由于酷刑、大量处决、强迫劳动和营养不良,造成了将近当时25%人口(约200万人)的死亡,其中有约40万人被柬共当作革命敌人杀害、死于各省的监狱之中;屠杀人口中包括了20-30万华人、占柬埔寨华人总人数的一半,此外25万伊斯兰教徒中有9万人死亡,而2万越南裔人则全部死亡。1978年,红色高棉在越南境内进行了巴祝大屠杀,导致了柬越战争激化,1979年初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被推翻、大屠杀结束。此后,各方在柬埔寨全国境内发现了超过两百个万人坑,这些地方后来被人称为“杀戮战场”。考虑到红色高棉的统治时间之短,其造成的死亡人数因此成为世界历史上最高纪录之一。1980年起,原S-21集中营被改建成了纪念大屠杀的吐斯廉屠杀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1952年起,波尔布特多次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军政训练(譬如游击队训练)以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等。1965年11月-1966年2月,波尔布特访问中国,中共高层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波尔布特讲述了“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枪杆子里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共产国际”等理论。他还会见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以及彭真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康生等人则向他介绍了一套铲除内奸的“理论”。
1970年,朗诺等人发动了政变、建立亲美的高棉共和国,西哈努克流亡中国,与此同时波尔布特跟随北越总理范文同访华。在中国共产党的协调下,红色高棉转而宣布支持西哈努克,中国是军事物品的主要供应者,仅在1970年,中国运往柬埔寨的军用物资就达400吨,卡车50辆。1974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西哈努克和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英萨利,谈到了柬埔寨解放后的政权建设问题,并且对红色高棉的方针表示赞成。
1975年6月21日,波尔布特访问中国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亲自向他传授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波尔布特推荐了姚文元写于1974年的两篇文章——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此后还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毛泽东认为:
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波尔布特则对毛泽东说:
毛主席同我们谈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带战略性的问题。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你的话去做。我从年轻时起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有关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导了我们全党。
另一方面,对于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实行的激进共产主义路线,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75年8月26日在医院会见即将返回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以及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英萨利等人,提醒到: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曾经犯过错误,我们必须为此造成的后果负责。我冒昧地提醒你们,不要期望通过一场大跃进就能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必须小心谨慎,明智行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共产主义道路。你们现在的目标不应当是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而应当缓慢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果你们抛弃这种审慎和共产主义的常识,那只能给你们的人民带来灾难。共产主义应当意味着人民的幸福、繁荣、尊严和自由。如果有人不顾人民的思想水准和民族现实,想一步就完全共产主义化,那无疑是冒险把国家和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我提醒你们不要再犯中国同样的错误。
据学者统计,仅在1975年,中方就向红色高棉提供了至少10亿美元的无息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2000万美元其它“礼物”。红色高棉统治的柬埔寨几乎完全依靠中国的物资、技术和专家的帮助才得以生存,中方人员帮助柬埔寨重建工厂、修复基础设施,同时也提供了军事援助。有学者估计,在红色高棉获得的外国援助中,中国提供的至少占90%。
附录:知乎用户Canicularis有关红色高棉和黑木崖势力的想法
171.在广东土改时期,华侨们因为通常拥有较多的现金资产,便成为了运动中的重点斗争对象。
在开平县平原乡,华侨吴奕悟因为夜间出门大便前没有打报告,就被找到理由进行了一番“斗争”,并被罚款5000万元。
结果工作队一看她这么容易就答应了交钱,就又暗示群众继续斗争,要再罚出1亿元。群众们便又对她进行了一番“猛烈斗争”,导致她在次日因伤重不治而亡。
另一位老华侨谭裔柏,在美国做了四十多年的洗衣工。年老落叶归根,返乡在家耕种着八斗田,一直到1949年时因为年老体衰,才将土地出租收了两斗谷,结果就被算了1100万的“剥削帐”。
这个老华侨之后因为害怕再遭清算,便在次年以74岁高龄重新去了美国,走的时候发誓再不寄一个钱回国。———《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东土地改革研究》
159.红色高棉中央常委的一张合影照片,从左至右分别为波尔布特、农谢、英沙利、宋先和藩蒙,以及一辆奔驰轿车。很显然,在全国范围与资本主义进行战斗的同时,并不妨碍领导人继续乘坐资本主义的豪华轿车。

147.有一年春耕季节,恰好有一个赶集的日子,许多农民不下田去赶集,使得驻村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员极为愤怒。而去赶集的人中恰好有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地主,尽管老地主早就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但是路线教育工作队还是认定是老地主煽动农民去赶集,破坏春耕生产。到第二天晚上,生产大队召开大会批斗老地主,老地主站在大队礼堂舞台的一角接受批判,中途老地主支撑不住,由地主的儿子代替他站在台上接受了一个多小时的批判 (由于老地主身体不好,平常对四类分子的训话和劳役大多数由他的儿子代替,而这种做法在当年的农村相当普遍,以至于中共中央的一个文件中曾经批评这种作法)。批判老地主的效果显著,农民的出工率迅速上升。其实在集体化的年代,农民对集体生产并没有积极性,不出工而去赶集与老地主完全无关,工作队只是拿老地主来杀鸡吓猴,因此这件事情给笔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级初探》.李若建
138.作为红色高棉领域的权威专家之一,Ben Kiernan的这本著作是目前对红色高棉在1975-1978年统治时期描述最为详尽的著作。在其五百多页的内容中,通过对成百上千位幸存者的采访,为读者们勾画出了这个恐怖政权的真实面目——在其统治下,有近170万柬埔寨人死于非命,其中一半是被该政权直接杀害,其余的则是死于超负荷的强迫劳动与严苛的食物配给。
这期间不仅是柬埔寨境内如华裔、越南裔、占婆裔等少数民族遭受了巨大的苦难,那些被认为是红色高棉政权基石的“旧人”,既贫困的高棉族农民也遭受到了同等的对待。尤其是在1978年初开始武装反抗红色高棉的东部地区,当地的平民更是遭到了该政权灭绝性的屠杀。
在书中作者还驳斥了将红色高棉视作一场来自底层农民反抗的传统观点,事实上红色高棉的中高层领导几乎全部出自该国在战后培养出的精英知识分子。就和之前的同类运动一样,柬埔寨的农民在其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境地——他们在内战时期被动员起来成为了红色高棉的主要兵力来源,这一时期农民与红色高棉之间还保持了较为融洽的关系。
但在进入金边之后,政府就立刻转变了对待农民的立场,原本的乡村社会被打破,农民的财产与自由遭到侵犯,所有的劳动力都被集中起来进行各类强迫劳动——这一切都是为了红色高棉的“宏大愿景”而必要的牺牲。当时间走到1978年时,即便是曾经最忠诚的农民群体也开始仇恨红色高棉。而随着越南军队的入侵,在各地都发生了农民向干部复仇的群体性行为,而已经落败的红色高棉军队也不忘对农民进行报复性的屠杀,这也象征着一场更为漫长的内战即将降临这片土地。
137.“上世纪大跃进时期,潮汕有谣曲这样唱:得罪干部上兴梅,得罪炊事食淖糜”。上兴宁和梅县客区干什么?大炼钢铁呀;淖糜又是什么?极稀的粥呀。那时食堂的炊事就有这权力,同样一勺子稀饭,分量不会少你的,可稠淖全凭他的好恶。在那会饿死人的年代,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潮菜天下》.张新民
136.随着韩桑林等人于1978年在东部专区发动了针对红色高棉中央的叛乱,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也进入了最恐怖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屠杀对象已经不再是某些特定人群,而是针对整个东部专区的平民,红色高棉将该地区上百万的平民都视作叛徒,并且发动了灭绝性的大屠杀。
当时在首都金边,一位华人亲眼目睹了红色高棉将城中6000多名来自东部专区的平民驱赶上了三条轮船,然后当船行驶到湄公河中时立刻向其开火并击沉了这三条船,船上的6000多人全部遇难,流出的鲜血染红了整条湄公河。
这位华人之后又与7000多人一起乘火车被送到了西北的菩萨省。等火车一到目的地,车上就有3000多人被红色高棉的士兵当场杀死。他能够幸免于难多亏了他的华人血统,那些士兵向他解释他们不想伤害华人,只是不得不杀掉那些来自东部的旧人。
当时还有一位生活在菩萨省的占婆裔妇女也回忆道,在1978年中旬时,她所在合作社被送来了3000多名东部专区的平民。在一开始这些人就被按年龄分成了不同的组进行劳动。而在过了两个月后,大屠杀开始了,这些人被按照年龄依次带去处决。本地干部告知她东部专区的所有人都已经“病态”了,他们必须将这些人全部清洗干净。在这三千多人中只有一个百来人的小组因为被安排的工作地点偏远而幸存了下来,直到越南军队解放了本地。
另一位当时生活在巴坎的人回忆,当时有700多位来自东部的平民被安插在了他的合作社。他打听到这是因为据说东部的人都在盼望越南人的到来。很快这七百多人就在一天夜间被集体枪杀,尸体被丢进了早已准备好的沙坑,其中一些受了伤暂时还没死去的人也一起被活埋了。
一位在1975年从金边被疏散到豆蔻山脉的人也供述道,在1978年上半年有许多来自东部的人被安置在了附近的各个合作社。本地的红色高棉士兵将这些人全部视作叛徒,几乎每天都会随机拣选一些人带出去处决。在经过了四个月的杀戮后,仅有极少数的妇女与儿童幸存了下来,因为越南军队在那时已经推翻了红色高棉的统治。
此人还亲眼目睹了一次大规模杀戮,当时有一千多名来自东部的平民被蓄意安置在了一处没有水源的山地。在饥渴的驱使下,这些人不得不冒险下山向士兵们哀求给他们更换一处地方。结果士兵们直接向着人群开火,当场就射杀了数百名平民,接下去人们用了几乎一整夜的时间清理尸体,那些暂时没有死去的人又被红色高棉的士兵用刀子砍死,他们身上的衣服被剥下分给了其他平民,然后尸体赤条条的被扔进了沟渠中。
一位生活在马德望的妇女也证实道,从1978年年初开始,就不断有来自东部的平民被安置到本地。红色高棉公开的说法是越南人正在炮击东部地区,造成了当地的粮食短缺。但在私底下,士兵告诉她这些人全是不值得信任的“叛徒”。
在一开始,红色高棉会带走家庭中的男性,宣称说要集中到另一个地方进行集体劳动,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回来。然后过了两个多月,红色高棉又告知那些妇女,让她们收拾东西准备与他们的丈夫和父亲团聚,但事实上这些妇女都被牛车带去了本地的一处仓库,然后在里面被用斧子和棍棒处决。
附录:知乎文章《“太行经验”指导下的山东土改》
来源:知乎用户Canicularis
1947年中旬,随着战争的白热化,各根据地的土改工作也被要求增加强度。之前土改不够坚决的山东遭到了华东局的严厉斥责,被批判为“富农路线”、“在执行方法上是限制群众路线”。
为了指导山东进行正确的土地改革,华东局在7月7日下达了名为《关于山东土改复查的新指示》,指示中要求在之后的土改复查中“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提出要“根据90%的农民的意见行事,如果党的规定与90%农民的要求不符合,就修改党的规定”,其眼下之意就是给出了10%的“地富分子”指标以供斗争。同时还介绍了兄弟解放区的“先进经验”,既之前太行区土改杀人、扫地出门的经验。
而随着这份指示传达到基层,更是变成了“地主一切都是非法不合理的……实行扫地出门,贫雇农小组成立与整理了农会,就要真正当起家来,不能把当家成了空话,一切照百分之九十农民的意见要求行事,对地主有生杀予夺之权,任何人不能干涉。”
在这样的指示下,许多干部就理解为之前减租减息是向地主“要粮”、土地改革是向地主“要地”,而土改复查就是向地主“要命”了。而被动员起来的农村“积极分子”们,更是直接将杀人当成了唯一的考核标准。很多村庄为了争功、得奖旗、受表扬,就开始挖空心思抓特务,扫地主、挖蒋根拔蒋毛,开会动员时“不是棍子会就是杀人会。而由于山东许多地区都属于根据地,大部分地主在经历了减租减息之后土地已经所剩无几,即便全部斗争了也拿不出多少用来“动员”,因此各地就以“抓特务”的名义开始乱捕乱杀。
由于死刑权被下发到村,各地都发生许多既荒唐与可怖的现象:在莒南县大店区,据当时的一位民兵庄某回忆:
“地主家有很多官服,农教会长穿上官愿坐堂,严重的时候枕木一敲,“给我把耳朵割了!”说用刺刀截就戳死了,死了好几百口子……我那时当民兵,负责从村里往北河带人,把人带去就回来,我不敢看。会开了些日子,白天开,晚上点上汽灯开。在牟家官庄杀很多庄家地主,外边小庄子里有50亩地的也得斗,瘸子里拔将军不是?
没地的破落地主也得杀。有很多是因为自己认为没罪恶没跑就被杀了。牟家官的庄惠顿有百十亩地,假装成医生跑了。他老妈妈在家.这个老妈妈平时谁家生小孩,就今天送小米,明天送面,后天送几个鸡蛋。村里开斗争会,村干部想砸死她,说他没炮的儿子都砸死了,还剩下她吗?让大家提意见,有个人说俺媳妇生娃的时候她送这送那。干部就说:“你坐下吧,还有谁提意见?”
刘家岭村的农教会长回忆道:
……张政务在会上讲了个例子,侍家宅子村有一家弟兄6个,都当石匠,三年盖了三层炮楼,全家四十亩地……瘸子里拔将军选出来了,弟兄6个大人被砸死,小孩被一劈两半……
历家寨村农救会长回忆道:
当时我记得村里地主就三五户,一复查就扩大了……47年我当农会主席,区里开反特复查大会,村里由我和老支书参加……会场上就打死好几个,有一个瘦巴的老头。
散会了回去,回来继续开会,开会就砸,那次五X虎的二儿当兵,要回来当天就砸死了。砸死了好几个,也有砸伤的,极左的,老妈妈、小孩齐上阵。五X虎是全区开大会打死的。除了五X虎爷俩,还有个老妈妈被打了,说她有钱,没拿出来,没打死。还有两家死了俩,枪毙两个,打死了三个。贫雇农当家作登的不轻了,有天晚上有个村有个别人说XX人不好,就乱棍打死了。
在日照县芦山区的三庄村,在动员后立刻就在村中发现了一个“特务机关”,村民郑全西只因从小在西安上学,又恰好从西安回来,即被认为是国民党员,当他闻讯带着全家逃跑时,就被敢去封门的人在家门外乱棍打死。
在另一个村,因为一个被关押的“特务”乘着看守睡觉逃跑了,于是第二天村里的贫农团就将村中的一个疯子与他的儿子一并打死交账。
大坡庄回去立刻成立了“贫雇农小组”,在研究后将八户人家扫地出门,有三个还没有打死押起来了,群众说“打不打不要紧了”,但干部却不罢休,开始“商讨如何打死好”。其中一个当过曾经顽乡长的人,被一再逼问是否有政治问题,最后被迫“供出”曾干过国民党后,就“拉出去揍死了”。然后又拉出去五个斗争,也不管招供不招供,参加诉苦会的一人一根把棍子,又拿出铁锨、撅头,一哄而上打死了。在追浮财时除了吊打之外,还把一些人绑在扁担上,并残忍地放在火上烤其胳膊窝来逼其说出钱财藏在哪里,为了让地主家妇女说出浮财,就把人往鏊子上烙(鏊子是当地做烙饼的工具),又刺手指。
滨海地委委员、民运部长在1947年11月28日的滨海地委扩大会议上检讨反特复查时说:“我们普遍杀,小孩也杀大人也杀,有的一个庄杀到四五十个,如大土山杀了四十多。”当时还有个村子,只因一个疯子说有特务支部、小组,即打死了28名所谓的特务,然后就连这个疯子自己也命丧棍棒之下。
孔家口子村因荣军人孔贤美联合村民反对有贪污行为的“村老虎”村长,两者产生矛盾。荣军人当民兵的弟弟偷了一口刀去找正在区里的村长而被搞起刑讯时说他哥是特务,这位荣军人随即被抓捕。送到区公所后被打得说胡话,咬了二十余人,结果这个只有80户人家的村子就抓出了43户特务。荣军人被打死后全村又被打死11人,其他也几乎被打死,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中贫农,只几家地主富农。事后群众反映打死的十一户中,只有三个该死。其余都是屈死的。
上大峪村一开始搞出一家特务,最后却咬上了60家特务,上古崖村也咬出60多家特务。沈瞳区南鲍瞳村一个中农只因他之前的外号叫“皇帝”,分区干部听到后即不问青红皂白把他给斗了,结果全村其他四十余户中农都吓得不敢过日子。
莒南县长、县委委员高风林在1948年滨海区的土地会议上也曾说过个乱攀咬的例子,当时潘沙沟48户人家,有45被咬成了特务,党员也没能幸免了。
官庄乡召开农代会议,在会上决定打死32个所谓的地主特务,民兵带着大棍把人押到这所谓的“乡农民法庭”,审问之后就拉出去枪决了。在这次会议后下面也有样学样,高家沟村原来只打算打死一个,回去后一次就打死十一人。台庄村竟然“光选些小孩做法官”,各村都照样子学,干部一见面就互相问“您庄打死几个?
在这种为了杀人而开设的法庭下,芦山区一口气就打死了160多人,该区南部的四个乡顿时觉得自己落后了,也纷纷表态一定会“限期完成”。
望海区尧王城村,由于一批物资丢失,乡长看谁都像特务,于是就听了一个流氓的话,把该村在外逃难刚来家的五个老实村民扣押起来,乡长带头前后审讯了三次,期间有一个农民竟然被活活吓死。
到了八月后,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进逼,各地的基层干部也开始惶惶不安起来,生怕遭到报复,于是就产生了“一网打尽满河的鱼”的想法,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之前许多只是稍有嫌疑的人,都统统打死了事。
芦山区的区委书记马吉德当时听说城里地主反攻倒算得厉害,于是就决定北边四个乡先打死105人,凡是地主即全部打死。之后随着战事紧急,许多之前被扣押的人被干部视作况累赘和负担,因此就把所有与敌伪有联系的、特务地主的妻儿、伪保长、流氓等等一概打死,声称“上次打死男人,这次打死女人,总之是能打死的一定打死。”
三庄村之前分两批打死了10个所谓的特务地主、封建地主。还有一些流氓坏分子“群众”本来也要打死,在干部劝说后暂时留下了,但在这次则全打死了,全村前后打死20人,上吊投井7人。望海区的区公所把附近100多个地主富农押了户虎睡岭,在林子里第一天挑了11个杀了,第二天又杀了6个。
黄墩区的梁山乡,其前前后后也一共打死了45人,外加送到县里枪决的10余名“特务”,也足足杀了五六十人,但还是被认为“落后了”。
当时在日照县巨峰区马瞳村,有一位村民名叫丁立现,他的父亲早年就死了,母亲顶着女地主的身份领着一家人勉强度日。四七年夏天时因为国民党军队进逼,全村的人都奉命向着河南边躲避。期间他母亲因为裹了小脚走得慢,结果到河边时就被干部摁到河里给灌死了,她的两个闺女见状扑上去想去救母亲,结果也被一道摁到水里灌死了。
后来丁立现四处找他老娘,结果被那位凶手威胁说“连你弄进去!”而他的母亲和两个姐姐并不是仅有的受害者,当时全庄有34个人都因为类似的原因被杀害。
巨峰分区的委员袁培瑞,在他同另一乡的干部交换意见说你乡打死多少他就打死多少。该乡石桥官庄一夜打死十二人,即是他强令打死的。在他带领下口要杀人都由干部小组长动的手。干部又下命令,谁不砸就与地主同罪,杀人的时候全村硬逼出五十余人开会,干部动员说“不砸死,来了敌人不和咱一条心,留一个一个刺眼钉。”还举例子说“崖头打死得多立功”指导员李克楷说,“咱敢不敢?”下边说“敢”就这样拉出打死了。
当时望海区有一位颇有名望的士绅名叫郑振东,他他创办过新式学校,积极投身于抗日活动,日照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还被选为县参议员。但在斗地主时由于当地强调按政策办事,这样一位爱国士绅即被害死了。芦山区三庄乡范家楼范聚东是当时著名的开明士绅,知书达理,抱有极强烈的爱国热忱,在抗日战争期间倾力支持中共抗日,为中共党和军队输送了大批的青年才俊,他生活居住的村庄范家楼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小延安”。但就是这样一位著名人士,仅仅因为在村里得罪了极少数人而在土改复查中被报复打死,而他那位已经做了藏马县农会主席的儿子范熙彭却爱莫能助,唯一所能作的即是“来信脱胎换骨,不承认父亲。”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清下,神经紧张的村民几乎看到任何陌生人都有特务嫌疑。当时有人走路者带了匣枪,就被捉去即以特务罪名打,有区队到石墩送信,虽然互相都认识却因无路条被打”。秦滩井村一妇女说“如割韭菜,一茬一茬,早晚挨着了。
在斩草除根的思想驱使下,有些地区只要家中有人涉嫌与国民党有联系,就会将其全家杀害。芦山区官庄乡高家沟打死的十一人里有两户为贫农,这两家老小一共被打死六口。之后村干部又怕其在区中队的两个儿子报复,威胁要带回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区干不同意,乃逼其二人表明态度才放过。大坡村通过刑讯逼供使一村民假供自己是国民党并咬上其他庄的几个人,当场有人说“这些人国民党来了不会与咱一心,非打死不行”,于是连他一共五个人一上场,群众一拥而上乱棍打死。该村一村民只因其儿在国民党当兵,“群众怕,即砸死了”。
由于胡乱攀咬成风,许多干部自身也成了受害者。滩井乡林家滩井村中的党员本就分为两派,当时一个被押地主咬上了其中一派的农会会长就三青团成员,另一派的干部就立刻将其逮捕,计划将其兄弟打死,后经区干发现方才救了这位农会长一命。
在当时,村民之间任何微小的嫌隙都会演变成杀戮。巨峰区马庄乡崖头村的农会主席只因自家小孩与组织出夫有功的村团长的小孩打架,即“主持要斗他,组织了十九个出夫开小差者将他打了,喊着要枪决,幸乡长知道禁止”,但这位村团长仍被“扫地出门”。石桥官庄李克枯与李茂父同为贫雇农,只因争山场时被李克枯争去,李茂父怀恨在心而乘开会之际呼口号:“这是正式坏蛋”,就这样李克枯在会场上被打死了。
沙沟村原村干郑培延因与村民郑培夫的母亲不睦,就诬称郑培夫散布谣言说“中央军进攻啦”,开会时非要将其弟兄四个都砸死,并威胁村干不能阻止“群众翻身”。在斗的时候,只郑培延自己提了一个意见,马上持一口大刀即杀了二口,当夜共杀了九口。接着郑培延追问群众:“彻底不彻底?”群众反映差不多了,但郑培延说:“不彻底啊”这样群众害怕了,还不知道要杀多少。第二天早晨去检尸跑了一个(郑培夫之五弟)但还是被上河提回又杀了。
附录:知乎回答波梗好笑在哪里?
来源:知乎用户Canicularis
最好笑的就是简中互联网上部分群体针对这段历史的超高强度造谣,他们大概是想用这种信息污染的方法来扭曲这段历史:
谣言一:
看到了金边有两百万人,但是认为只要柬埔寨向大国磕头就可以拿到粮食了。
事实:柬埔寨不需要磕头也拿到了粮食,红色高棉四月占领金边,而外国的粮食援助就五月就已经送到,外国势力还贴心的送上了包括衣服、药品、农药、铁路设备、燃料等等一切用于维系国际运作的物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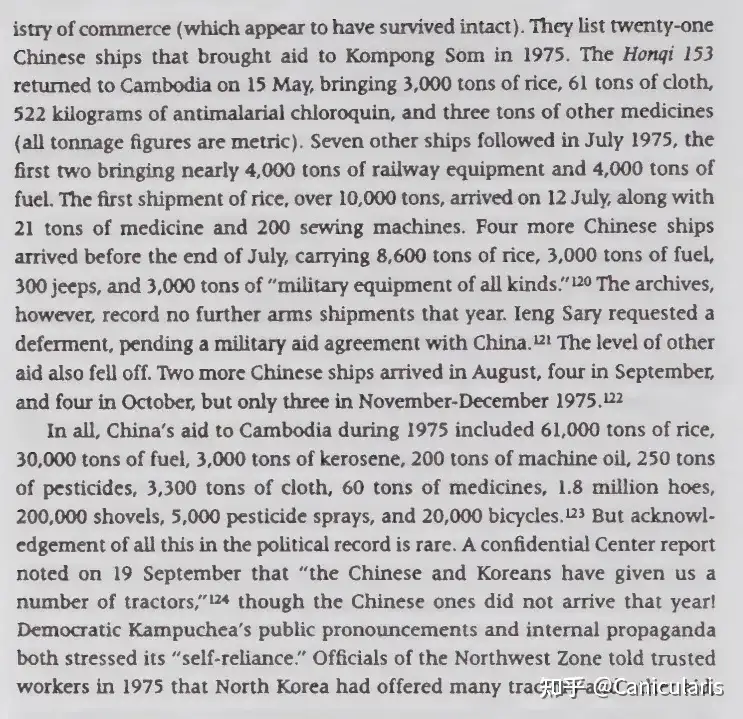
谣言二:
无视金边两百万人挤在一起,真切的认为波波去城市化是为了搞原始主义
事实:波尔布特早在占领金边之前就已经制定了清空柬埔寨全国城镇的计划,这并非只是针对金边,凡是能称得上镇子的居民点都被清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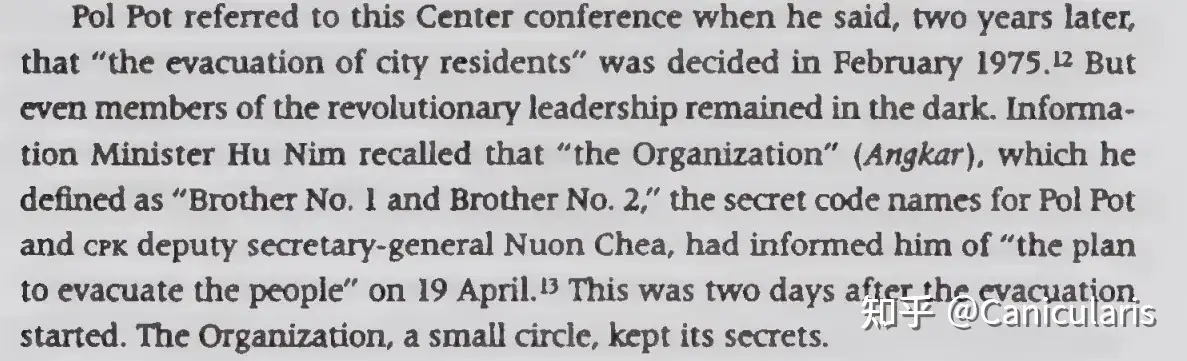
谣言三:
觉得只要波波不去袭击越南就不会打起来,在中越边境跳腾的黎笋在对柬埔寨问题上居然能如此冷静,难道柬埔寨比我们还厉害?
事实:是柬埔寨主动在1977年初挑起了对越战争,并对越南领土上的柬埔寨难民与越南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才让越南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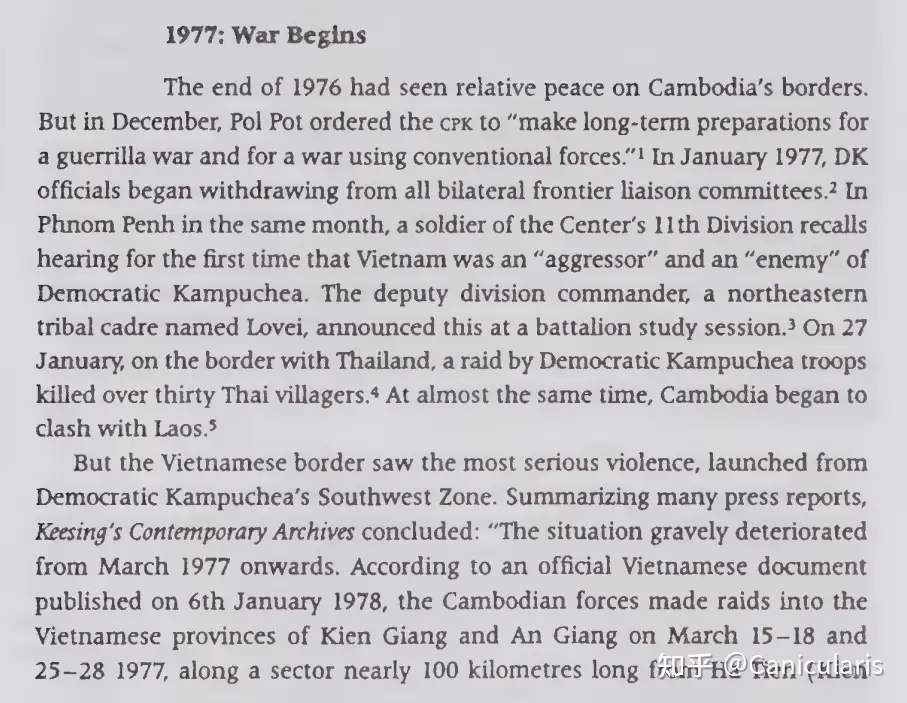
谣言四:
4.自由党国际成员,柬埔寨烛光党(救国党)至今仍在给波波辩护,认为这是越南人制造的谎言。
事实:这个谣言是红色高棉在被越南人赶出金边后为自己辩护而散播的,但S-21的主官康克由在2009年接受国际法庭审判时就特意反驳了这条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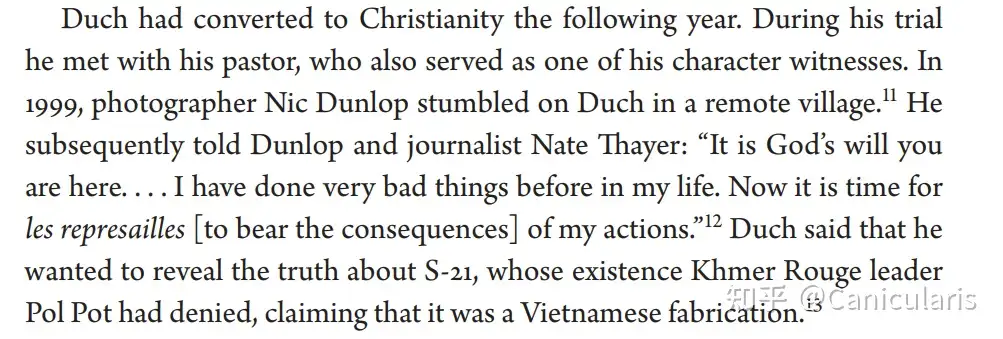
谣言五:
两百万的出处居然是电视剧《第五共和国》里车智澈说的,我愿称之为虫豸计数法
事实:这段话属于是在自曝其丑。学术界对红色高棉在1975-1979统治全国期间造成的死亡人数认定是170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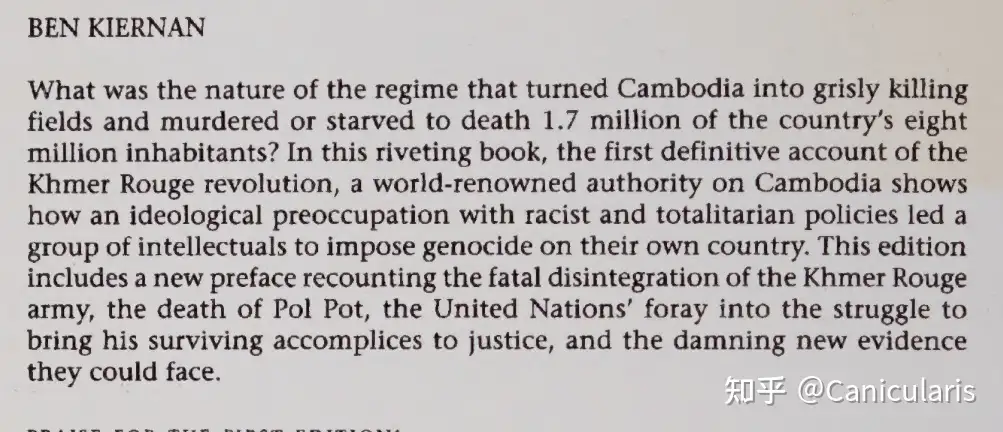
谣言六:
韩桑林也参与了图图,但是没人骂他。
事实:有大量的证人可以证明,韩桑林所属东部专区的是当时纪律最为严格,也最人性化的武装力量,早在红色高棉用暴力驱逐金边市民时,就发生过多次这支部队为了保护民众而与红色高棉的嫡系部队发生冲突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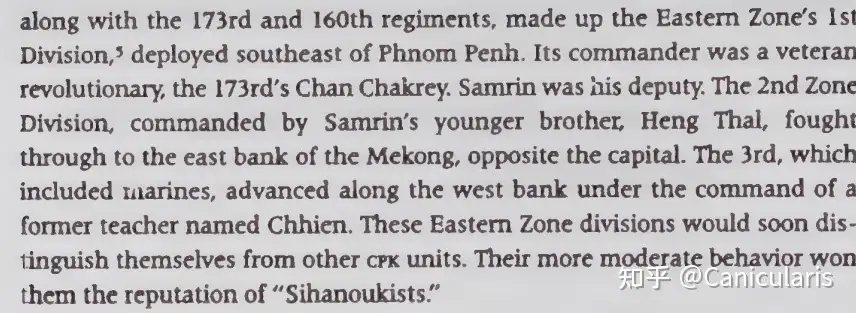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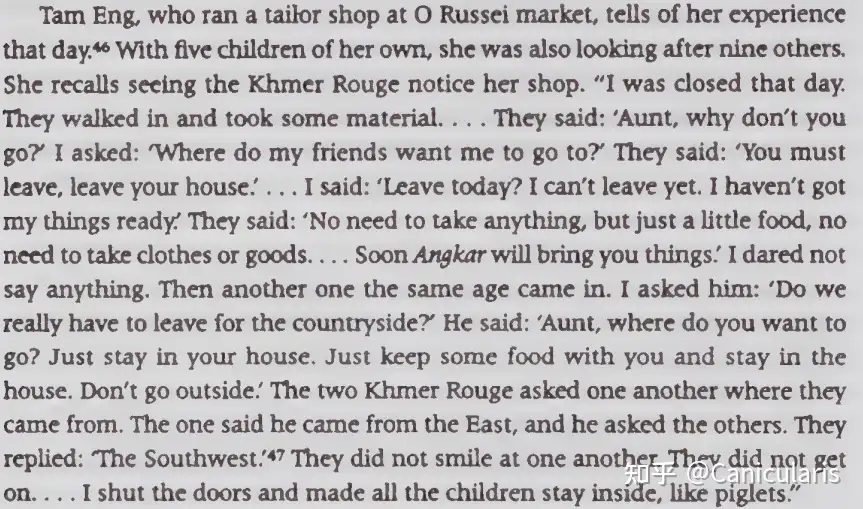
附录:俄国人的劣根性
《财富、贫穷与政治》第3章<文化因素>信任与诚实
尽管信任能促成对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合作方式,但信任如果缺乏诚信必定是一场灾难。一个社会的诚实度框定了这个社会的信任半径,造成的经济影响超过许多有形优势。
例如,苏联即便不是地球上自然资源最富集的国家,至少也是其中之一。苏联也是仅有的工业国中石油储量极其丰富的国家,甚至是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国之一。它土壤肥沃, 享有盛名,并且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平原。102苏联的铁矿石储量也是世界第一,森林覆盖面积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拥有世界第二大锰储量103和世界三分之一的天然气储量104。 除此之外,在许多年里,苏联作为镍生产国也领先于世界105。在几乎所有自然资源上, 苏联都能自给自足,并且出口了大量的黄金和钻石。到1978年,全世界接近一半的工业级钻石都是由苏联生产的。106
然而,根据两位苏联经济学家的研究,虽然苏联拥有这些有形的自然资源优势,民众也接受了良好教育,苏联的经济在效率上却远远不如德国、日本或美国。107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欧、美国或日本,而日本是世界上资源最匮乏的国家之一。
如此受自然青睐的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平为何会低于许多自然资源不如它的国家呢?苏联的存在简直就是为了反驳地理决定论。抵消苏联在自然方面优势的其他影响因素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文化方面的。回到19世纪,当苏联还被称作沙皇俄国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针对阻碍其经济发展的文化障碍是这样评价的:
官员普遍贪污腐败,这制约了沙皇俄国的经济发展能力:因为官员的报酬取决于他们能否成功地让人们的烦恼翻倍,这样人们才会为免除烦恼向他们行贿。108
腐败带给经济体的成本不只是行贿的金钱或被官员窃取的钱物,甚至主要不是这些。 最主要的成本是没有发生的事——没有开始的商业活动、没有进行的投资和没有发放的贷款。在一个极其腐败的经济体中,这些经济活动的回报率必须高于个人的努力成果不容易被剥夺的经济体,这样人们才会去做。
19世纪晚期,沙皇政府试图让俄国经济更加现代化,并邀请西方企业来俄国开展商业活动,这些企业会雇用俄罗斯人做工人,慢慢也会雇用俄罗斯人做管理者,但他们从不雇用俄罗斯人做会计。不只俄罗斯人当会计是个问题,20世纪初的一位法国观察家曾友好地指出,俄罗斯人当管理者在经营中也会造成非常多的浪费。109在俄罗斯,“像德国人一样诚实”和“像德国人一样守时”110曾是常用语,表明俄罗斯人自身很少具备这些品质。 过去的文化差异到了今天为什么是这样的,又是如何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会迷失在时间里,但这类文化品质对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
普遍的腐败在俄罗斯延续了下来,甚至在斯大林统治下也存在。尽管有诸多惩罚——包括遭受劳工集中营的奴役。苏联经济中有一群被称作“中介者”(tolkachi)的人,他们主要为企业从事非法活动,这些企业在官方许可的有限活动中受到严格限制,很难完成莫斯科的中央计划制定者给他们设定的目标。111
在沙皇俄国时期普遍存在的腐败在整个苏联时期都没有消失,也延续到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一家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股价仅相当于美国同类石油公司股价的1%,因为“市场 预期俄罗斯石油公司会受到内部人士有组织的劫掠”。112根据一家俄国报纸的报道,要想被一些声誉卓著的高等院校录取,需要行贿1万到1.5万美元。据该报估计,每年俄罗斯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的此类支出至少有20亿美元。
俄罗斯以其自然资源富集和生活水平低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113,告诉我们有形因素的优势如何被不利的无形因素制造的障碍所抵消。当然类似情况不只发生在俄罗斯一国。普遍的腐败使得开发自然资源所需的大额投资风险过高,结果就是不论本地还 是外国投资者都不愿意冒险一试。
但是在其他情形下,信任半径能让某些特殊群体富裕起来,而且不只是在繁荣的国家,很多是在法律体系不可靠又腐败的第三世界国家。一些群体如印度的马尔瓦尔人或东南亚 华人中的小群体,即使没有合约或不具有主流社会的法律或政治制度,他们也可以彼此从事金融交易。在正式的法律体系无效或腐败的国家,这是一种独特的优势。因为它给予了 群体成员更大的信任半径,使得相对于群体外部的人,他们的经济决策更快捷,风险也更小。
在更发达的经济体中,特定群体内部的高信任度同样是一种优势。例如,纽约的哈西德派犹太人根据口头协议寄售昂贵的珠宝,并基于非正式协议共享收益。114印度的马尔 瓦尔人在国际贸易网络中也这样做115,东南亚华人的小群体也有同样的现象116。另外, 西非和西半球部分地区的黎巴嫩人小群体也有类似的贸易模式。117
《财富、贫穷与政治》第3章<文化因素>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很重要,它不仅能够在物质资本遭受毁灭性破坏后帮助一国迅速恢复,例如战后重建;它在正常年代的经济进步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我们与穴居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力资本。
有些人倾向于将人力资本等同于教育。毫无疑问,教育是人力资本的一种,我们也经常粗略地用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但应当指出的是,许多人力资本是在学校之外获得的,此外一些学校教给学生的技能很多不是市场需要的,个别学校还会以负面态度、错误预期和厌恶之情等形式产生负人力资本,对经济产生不好的影响,因而学校对学生人力资本的开发贡献很少,甚至为零。鉴于教学内容不同,教育有时会让人对进入私人部门工作产生反感,或拒绝从事任何不满足“有意义的工作”这一定义的事,这里的“有意义”是指那些能够让人心满意足的工作。
开创工业革命的人大多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他们都是有实际工作技能和经验的人,而非精通科学的科学家或系统研究过工程的工程师。在正式的科技研究普及之前,工业革命已经在进行中了。甚至后来的工业先驱如托马斯·爱迪生和亨利·福特接受的正式教育也很少,怀特兄弟高中就退学了。到了电子时代,比尔·盖茨和迈克尔·戴尔均是大学肄业生。总之,人力资本不等同于正式的学校教育。
人力资本可以表现为教育之外的其他形式,教育普及也不意味着同样的人力资本普及。 21世纪的俄罗斯被称作“高教育水平和低人力资本的社会”122。从更直接的经济角度看, 俄罗斯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口大约占全世界的6%,但在全世界新专利和专利申请量中仅占0. 2%。1995年到2008年间,德国、日本和美国发明的专利大约分别是俄罗斯的60倍、200倍 和500倍,甚至新加坡这样的小城邦国家的发明专利也比俄罗斯多。123
附录:魁奈对斯密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家对儒家有误解,其实儒家反而影响和启发过西方
对于自然形成的市场秩序,最佳状态是应该不加干涉,即“善者因之”,其次才是进行引导和教导,“最下者与之争”,最糟糕的情况便是朝廷去与民争利,其实是批评当时的盐铁垄断和均输政策,其态度与贤良文学是一致的。过去一些主张自由市场的西方经济学家对儒家的经济思想有误解,如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就认为,儒家与法家接近,而老庄才主张自由经济的,鲍芝(David Boaz)也认为,老子是第一个自由经济的主张者。但实际上,随着认识的深入,已经有西方经济学家指出,根据《论语》《孟子》以及《盐铁论》等文献中反映的儒家思想,恰恰是主张自由经济和商业传统的(Roderick T.Long;Austro-Libertarian themes in early Confucianism.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Volume 17,no.3(Summer 2003),PP35—60)。
可以说,儒家思想的经济底色既不贬低商业活动,更不是主张“抑商”,而是尊重市场的基本自然法则,体现为“无为”。这一思想,在近代传播到欧洲,并对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的法国重农学派曾产生过积极影响。如魁奈(Francois Quesnay)就曾通过西卢埃特受到过“中国哲学家的书籍”影响,并且颇为崇尚儒家思想,而西卢埃特是在1687年从孔子的著作中获取到了关于“听从自然的劝告”,“自然本身就能做成各种事情”的观点,由此联想到以天道观念为基础的中国“无为”思想,有助于对西方自然法的研究。英国学者赫德森认为魁奈的自然秩序思想就是中国主张君主“无为”的观念,日本学者泷本诚一认为法国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观念与中国思想相同,我国学者侯家驹也曾指出“我国儒家经济思想启发了西方自由经济思想”。谈敏先生认为,儒家主张的无为,以治理为目的,尤其讲究德治,这对于魁奈当时正在积极寻求一种新的经济原则,以此取代他所坚定反对的国家干预型重商主义政策来说,显然产生了很大启迪作用。综合考察来看,“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原则,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儒家的无为思想之变形”(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212—214页)。
附录【李竞恒】《儒家的商业观,和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古老的商业文化,重视财富
商业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周易·系辞下》记载说在遥远的神农氏时代,就出现了原始的市场,“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商人”“商业”词汇的来源,便是擅长经商的商民族,《尚书·酒诰》说商民族的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他们驾驶着牛车到远方经商,赚钱孝养自己的父母。商民族的祖先首领王亥、王恒等人,也是擅长经商的,《周易》大壮、旅卦分别提到他们“丧羊于易”“丧牛于易”,赶着牛羊四处经商,遭到有易部落的袭击而丧生。部族首领亲自经商,甚至为此而死,说明商民族有重视商业活动的传统。商代金文族徽中,有些是人背贝串的图像,代表了以贸易为职业的氏族,以商贸为族徽,也显示了商业具有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三联,1999,第382页)。商亡国后,商王畿地区的遗民仍然擅长经商,如殷遗民的聚居中心洛阳,在周代发展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的商人“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遍布各地,十分活跃。在一般民间,如原商王畿的卫国,商业活动也活跃,人们熟悉的《诗经·卫风·氓》,就描写当时卫地民间“抱布贸丝”的商业活动,而著名的儒商子贡也出生于卫,当是受到此种风俗的熏染。
孔子为殷人后裔,应当也对商业文化并不陌生,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孔子反复说“沽”,使用商人的语言,说明他对市场非常熟悉(余英时:《商业文化与中国传统》)。和一般人想象的陈腐穷老头形象不同,孔子本人并不敌视商业活动和富贵,他认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富有是值得追求的,所反对的只是“不义而富且贵”,而“富而好礼”(《学而》),则是他最赞赏的模式。《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曾笑着对爱徒颜回说:“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希望颜回能够富有,自己来担任其管家。这也可以解释孔子对其爱徒子贡的态度,他将儒商子贡比喻为“瑚琏之器”这样的宗庙宝物(《论语·公冶长》),而不是将其批评为“满身铜臭的财主”,就很能说明原始儒学对于商业活动与财富的基本态度。
重视契约的传统,有时甚至拯救国家
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契约传统,但西周的郑国在立国时代,便和商人们建立起一项宪法性的契约,所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左传·昭公十六年》),意思是只要你们商人不背叛国家,那么国家就保证不强买你们的商品,也不会强行索取或抢夺。你们有怎样的巨额财富,都与国家无关。这一契约,在日后对保护郑国商人财产权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两百年后,势力强大的晋国权臣韩宣子向郑国商人索要一件玉环,郑国执政官子产以“这不是国家府库收藏的器物”为理由回绝了。韩宣子又用压价的方式,向商人强行购买玉环。这时,子产搬出了两百年前的这项契约,谈到了商人与国家的约定,国家有义务保护商人的财产权,否则“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最后,韩宣子只能放弃强买的打算。
子产坚持了郑国的古老契约,守护了商人财产,他能“养民”的德性,受到了孔子的高度评价,认为他是“惠人也”(《宪问》),“其养民也惠”(《公冶长》)。郑国有保护商业和财产权的契约传统,因此商人地位较高,也愿意维护国家的利益。最著名的便是弦高犒师的典故,公元前627年,郑国商人弦高到成周去经商,在滑国遇到了要偷袭郑国的秦军,为了保护郑国,他急中生智假冒郑国使者,用自己的十二头牛犒劳秦军,并派人回国报信防备,秦军认为郑国已有准备,便放弃了偷袭计划。
《左传·成公三年》记载,晋国的大臣知罃在邲之战中被楚国俘虏,有“郑贾人”试图将他藏在要贩运的丝绵“褚”中带走逃离,但还未行动,楚国人就将知罃放回去了。知罃想报答这位郑国商人,商人却说“吾无其功”,因为知罃是楚国人放的,自己没帮上忙,便拒绝了赏赐,又到齐国去做生意。从这里也可看出,郑国商人很讲究诚信,讲究无功不受禄。此外,他们经常参与国际间的政治活动,也说明社会地位不低,有一定道义和理想的观念。显然,只有长期生活在一个财产得到良好保护的社会,才会养成这样的品德和趣味,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
先秦时期的儒家,有时也以商业契约的思维,来比喻和理解君臣关系。例如清华大学收藏竹简的儒书《治政之道》中,就提出了“君臣之相事,譬之犹市贾之交易,则有利焉”(《文物》2019.9)。意思是,君臣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和商业交易相似的契约关系,臣带着礼物“质”寻找合作的君,双方达成合作契约,便通过“委质为臣”,建立起契约关系。通过契约合作,让君臣双方都获得受益。
孟子的商业思想,与亚当·斯密相通
到了战国时代,孟子对商业和市场也持开放态度。在《孟子·梁惠王下》,他提出治国需要“关市讥而不征”(在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在《尽心下》中,他提出“古者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意思是古代建立关隘,是为了保护社会,而不是为了多收税,他主张对民间商业不收关隘税。这一点与英国《大宪章》第13条,免除各市、区、镇、港的关卡税,皆享有免费通关权的主张是一致的(《大宪章》,商务印书馆,2016,第33页)。战国时期各国设立有很多的关卡收税,如包山楚简《集箸》简149就记载了七个邑、四个水道日常要收取“关金”,但是从战国时代的鄂君启节铭文来看,像鄂君启这样的特权贵族来说,又可以沿途关卡免税,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孟子的主张就是,各个关卡,无论贵族还是普通商人,都统统不收税,藏富于民。所以梁启超先生对这一主张的评价是:“儒家言生计,不采干涉主义”(《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90页)。孟子认为,只要能更好地保护民间商业,就会“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孟子·梁惠王上》),天下的商人都希望来这个低税率的国家,市场则会进一步繁荣。
孟子的另一项关于社会分工的思想,也是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哈耶克曾谈到,远古以来的人无法理解商业活动的实质。他们看到商业“贱买贵卖”,因此将其视为一种可怕的魔法。西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对商人表示藐视(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科出版社,2011,第101—102页)。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的原始儒学这里,就没有这种偏见,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对商业活动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而非蔑视。当时有神农家的许行,反对社会分工,带领其弟子自己耕田、打草鞋和织席子(《滕文公上》),对此孟子的态度是,既然许行戴的帽子、耕作用的铁农具,都是用自己种的粮食交换而来,那就说明了社会分工的必然性,没必要事必亲为,这也正是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合理性。许行还认为,理想状态是市场上所有商品价格相等,轻重相等的丝绸和麻布也都价格等同,就会实现社会正义。
孟子针对这种人为干预市场价格的谬论,提出这是乱天下的观点,如果大鞋和小鞋子都同一个价格,谁还去生产大鞋子?可以说,儒者孟子是为自由市场辩护的,而那位反对社会分工,主张干预价格的许行,根据钱穆先生考证,是南方楚地的墨家,禽滑厘的弟子(《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2,第408—409页)。
即使是战国晚期,出现了荀子这种比较法家化的儒者,也仍然重视市场分工和贸易的优势。《荀子·王制》中强调,中原地区能够得到北海的走马吠犬,南海地区的羽毛、象牙,东海地区的鱼、盐和染料,西海地区的皮革。水边的人能获得足够的木材,山上的人能得到足够多的鱼,农民不用冶炼能获得足够的农具,工匠不用亲自耕田却能获得足够的粮食,“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能产生这样神奇效果的,只能是充分发育的市场贸易和社会分工。
抑制和打击商业是秦朝和法家文化
在诸子百家中,儒学对商业和市场的态度最为肯定,而最为敌视商业和市场的则是法家。《商君书·弱民》提出弱民的主张,主张“利出一孔”,只有为君主耕战才能获取利益,而民间若能通过经商致富,即所谓“商贾之可以富家也”(《农战》),显然会削弱“利出一孔”的机制,民间便可以“皆以避农战”,不会为君主所用。在《垦令》篇中,商鞅将商人视为“辟淫游惰之民”,要“赋而重使之”,达到“商劳”的效果。主张“商贾少,则上不费粟”,认为商业活动是消耗了社会资源,要达到“商怯,则欲农”,“商欲农,则草必垦”,另一方面加重关口的税率,“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逼迫商人成为耕战之民。同样,韩非子对商业也极其敌视,他认为“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将工商业者视为可恶的游民,要让他们身份卑贱,因为商人“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韩非子·五蠹》),经商致富会破坏耕战的吸引力,削弱“利出一孔”的制度。
秦国坚持法家重农抑商的耕战政策,导致秦国几乎没有出现著名的大商人,如吕不韦是来自东方,并非秦人,而且在秦国的身份也只是参与政治,而非商人。又如《史记·货殖列传》中出现的两位“秦国大商人”乌氏倮、寡妇清,其实也并非秦人,而是属于受到政策优待的边境少数民族。乌氏倮是甘肃戎狄游牧部落的商人,通过给戎狄王送礼而得到便利,因而发财致富。巴寡妇清是西南巴族豪酋的子孙,经营祖传的丹砂矿致富,能“用财自卫”,即当地拥有部落武力的豪族,并非秦国的编户齐民。秦始皇为其筑怀清台,并非是重视商业,而只是笼络边境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权术而已。秦始皇对商人的真实态度是敌视的,在秦《琅邪刻石》中,他就吹嘘自己“上农除末”,即尊崇农业,打击了末业(商业),这才是秦皇真实的想法。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后附录有收入秦律的《魏奔命律》,其中提到对“假(贾)门逆旅”即商人和开客店者的仇视,要将他们全部抓到前线当炮灰,吃犯人的伙食,“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壕”(《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第294页),拿这些商人和店老板去填壕沟,当炮灰。
整个秦朝,儒家、商业社会都遭受重创。岳麓书院收藏秦简《金布律》中,规定“禁贾人毋得以牡马、牝马高五尺五寸以上者载以贾人市及为人就载,犯令者,赀各二甲,没入县官马”(陈长松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年,第110页),不允许商人使用高头大马经商,否则没收马匹并重罚款。此外,《金布律》规定,商贾如果在大路上做买卖,就会被“没入其卖也于县官”,当然,官府卖东西,则“不用此律”。刘邦集团继承了秦的基本遗产,继续执行“抑商”的政策,“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盐铁论·本议》),降低商人的政治地位。《史记·平准书》记载,“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不但用重税打击商人,并且规定商人子孙不得当官,不能乘坐马车和穿丝绸。应该说,汉代国家继承了秦朝的基本政治遗产和治理观念,所不同的是,汉初经济凋敝,又部分吸取了亡秦的教训,而官方的道法家思想虽然和纯法家思想之间具有共同渊源,但却更加灵活,可以在不全面启动秦制的前提下实行部分“无为”,以启动民间巨大的经济创造力。
到汉武帝时期,汉朝重新启动半休息状态的秦制,打击商人以汲取财富。元朔二年,强制将天下“訾三百万以上”的富商迁徙到茂陵,进行控制(《汉书·武帝纪》);另一方面是垄断盐铁经营,“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史记·平准书》),经过桑弘羊将其直属于大司农,进行全国性的垄断;并且实行酒类的国家专卖,“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汉书·武帝纪》);此外又对商人收取算缗的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两千钱就要上交一百二十钱作为财产税,其后又鼓励告缗,如果商人不如实登记和上缴财产税,有人告发,就可以获得该富商的一半财产。2013年在成都老官山西汉墓葬M1中出土的木牍,记载有“贾皆没入所不占”,“令诸郡国贾”等文字,正是对商人进行管制和打击的记录(《考古》2014.7),整理者认为这批简牍文书内容与汉武帝的算缗、告缗政策有密切关系(《考古》2016.5)。严酷的告缗打击,导致当时一半中产以上的人家破产(《史记·平准书》)。著名的铁器大商人卓氏家族、程氏家族,在西汉中期以后便没有相关的记载了,很可能便是在武帝的盐铁和算缗打击下,走向了衰败和灭亡。武帝死前将负责盐铁垄断的桑弘羊作为精心安排的托孤之臣,后来实际上仍然继续执行武帝的时政方针(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北京三联,2015,第27—28页)。
汉朝官营工厂效率低下,儒者主张“盐铁皆归于民”
面对此一困境,儒家士人的态度是反对此类抑商政策。早在武帝刚实行盐铁政策不久,儒者董仲舒就主张“盐铁皆归于民”,“薄赋敛”,将盐铁经营还给民间商人,并减少过高的赋税(《汉书·食货志上》)。在昭帝始元六年的盐铁辩论会议上,主要以儒家士人为主的“贤良文学”站在民间立场,高度反对武帝遗留下来的盐铁政策。主张盐铁垄断的官僚们赞美商鞅,垄断了山泽大川的利益,实现了“国富民强”。相同的道理,盐铁垄断也是“有益于国”的。贤良文学们则反驳,汉文帝时没有盐铁垄断,而民间富裕,而现在则导致了“百姓困乏”(《盐铁论·非鞅》);主张垄断的官僚们认为民营盐铁的商人是“不轨之民”,如果一旦“利归于下”,保障了民间能获取利益,就会“县官无可为者”。针对此说,贤良文学们强调“公刘好货,居者有积,行者有囊”(《盐铁论·取下》),强调古代的贤王从来不会与民争利。他们还指出,官府垄断的铁器生产,质量低劣,“县官鼓铸铁器……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盐铁论·水旱》),官府役使大量卒徒生产,这些被役使的劳动力也不会尽心,保证产品质量。官府生产的烂农具,价格还定得特别高,导致很多农民只能“木耕手耨”,用木头耕土,用手薅草。
汉代官府垄断导致铁器品质低劣,这也得到了考古资料的证实,居延汉简记录,铁官所造武器,弩口有伤洞,釜口缺漏。连军用铁器的质量尚且如此,当时农具的品质可以想象得到。而尹湾汉墓出土的木牍《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中,则记载了数量颇为巨大的库存武器,仅仅是一个东海郡的武库,就藏有五十三万多件弩、上千万的箭矢、十四万件甲、九万八千件盔、四十五万件铍、九万九千把剑等数量极其巨大,可以武装上百万人的武器。一个东海郡,显然并不需要这么巨大数量的武器。如此众多的闲置武器,也可以窥见官府铁器生产的规模甚巨,有庞大的生产计划,所谓“务应员程”,即“计其人及日数为功程”(《汉书·尹翁归传》颜师古注),但产品却是质量低劣,一般铁器不能卖出,只能“颇赋与民”,强行摊派,掠夺民间。而武器装备,则堆山填海地储存在各地武库中。最新考古资料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2017年在山东青岛土山屯147号西汉晚期墓出土木牍记载,元寿二年,一个小小的堂邑县,就储存了二十七万三千多件武器,而其中竟多达三万二千多件都存在质量问题,需要“可缮”(《考古学报》2019.3)。从这些迹象都能看出,汉朝官铁垄断的效率和质量非常低下。
针对官营盐铁的低效和扰民,贤良文学们强调了以家族为纽带的民营效率:“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盐铁论·水旱》),民营的家族企业,家人们同心协力,能够制作高质量的商品,品质低劣的产品根本无法流入竞争充分的市场。此外,贤良文学提出,“王者务本不作末”,“是以百姓务本而不营于末”,“天子不言多少”,看起来好像是看不起“末业”和赚钱,但其实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所反对的是朝廷垄断的“末业”,而非民间。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贤良文学此处真正所反对的,不是民间工商业,而是以盐铁、均输等重大措施,由朝廷直接经营的工商业。”(《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大学版社,2002,第86页)。
虽然盐铁论战未能战胜与民争利的制度垄断,但儒者有理有据地展现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到东汉儒学更进一步发展后,他们坚持的努力终于起到了效果。章和二年四月,朝廷下诏书,“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后汉书·和帝纪》),废除了盐铁垄断的制度,允许民间商业自由参与,这正是多年来儒者与社会一起努力的结果。
司马迁赞美商业和“素封”,是儒道合一的文化背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学者司马迁对商业的积极态度。可能一些人会说,司马迁不是儒家,而是道家或杂家。实际上,司马迁的学术虽然确有百家驳杂的色彩,但却又以儒学为基本底色。徐复观先生认为“他以儒家为主,同时网罗百家”(《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194页),应该是很准确的归纳。《汉书·司马迁传》说他“年十岁则诵古文”,清代学者王先谦注释说“史公从安国问”,意思是司马迁从小就跟随大儒孔安国,学习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先秦儒书。他关于《春秋》的知识则是“余闻之董生”,就是跟随大儒董仲舒学习《春秋》,后来他写《史记》也是模仿作《春秋》。在学术训练和知识传承上,受业于两位儒学名家,以儒学作为底色。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将孔子尊奉到诸侯级别的“世家”,并评论“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他将孔子尊为至圣,正是儒者背景的体现。周德伟先生曾谈到:“吾人须知司马迁乃儒学正统,孔子之大成至圣地位,即由彼所确定,其所言点点均符合孔子及以后圣哲之教……圣哲何尝不重视经济因素及人民之利。但反对以政治手段干涉经济势力的自然发展,则以司马迁表现得最明朗”(《周德伟论哈耶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4—165页)。
作为以为儒学为根基的学者,司马迁对商业和市场的态度与《盐铁论》中的贤良文学们相似。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并赞美了大量优秀商人和家族企业,如范蠡、白圭、倚顿、邯郸郭纵、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宣曲任氏、韦家栗氏等,他赞美儒商子贡,能通过巨大的财富和社会影响力“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子贡对儒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司马迁甚至发明了一个词汇“素封”,就像将并没有实际王位,但却行有王者之事的孔子被尊为“素王”一样,优秀的商人和企业家被他尊为“素封”。他指出,工商业和社会分工是必须的,而这一切会自然形成,所谓“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人们为了牟利,便会竭尽所能,参与市场分工。自由的市场一旦形成,便会“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社会变得繁荣。“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他的意思是,农民生产粮食,虞人运输物流,工人将原材料制作为产品,商人把产品四处贩卖,这些市场分工是自发形成的,根本不需要官府事先通过人为设计把他们配置在一起。根据自由市场的规律,价格的波动自然调配商品流动,就像水一样日夜不息地自然流淌,不用强制的行政命令,市场自然会将产品送到消费者面前。
西方经济学家对儒家有误解,其实儒家反而影响和启发过西方
对于自然形成的市场秩序,最佳状态是应该不加干涉,即“善者因之”,其次才是进行引导和教导,“最下者与之争”,最糟糕的情况便是朝廷去与民争利,其实是批评当时的盐铁垄断和均输政策,其态度与贤良文学是一致的。过去一些主张自由市场的西方经济学家对儒家的经济思想有误解,如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就认为,儒家与法家接近,而老庄才主张自由经济的,鲍芝(David Boaz)也认为,老子是第一个自由经济的主张者。但实际上,随着认识的深入,已经有西方经济学家指出,根据《论语》《孟子》以及《盐铁论》等文献中反映的儒家思想,恰恰是主张自由经济和商业传统的(Roderick T.Long;Austro-Libertarian themes in early Confucianism.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Volume 17,no.3(Summer 2003),PP35—60)。
可以说,儒家思想的经济底色既不贬低商业活动,更不是主张“抑商”,而是尊重市场的基本自然法则,体现为“无为”。这一思想,在近代传播到欧洲,并对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的法国重农学派曾产生过积极影响。如魁奈(Francois Quesnay)就曾通过西卢埃特受到过“中国哲学家的书籍”影响,并且颇为崇尚儒家思想,而西卢埃特是在1687年从孔子的著作中获取到了关于“听从自然的劝告”,“自然本身就能做成各种事情”的观点,由此联想到以天道观念为基础的中国“无为”思想,有助于对西方自然法的研究。英国学者赫德森认为魁奈的自然秩序思想就是中国主张君主“无为”的观念,日本学者泷本诚一认为法国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观念与中国思想相同,我国学者侯家驹也曾指出“我国儒家经济思想启发了西方自由经济思想”。谈敏先生认为,儒家主张的无为,以治理为目的,尤其讲究德治,这对于魁奈当时正在积极寻求一种新的经济原则,以此取代他所坚定反对的国家干预型重商主义政策来说,显然产生了很大启迪作用。综合考察来看,“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原则,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儒家的无为思想之变形”(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212—214页)。
附录:弗朗索瓦·魁奈
弗朗索瓦·魁奈(法语:François Quesnay,法语:[fʁɑ̃swa kɛnɛ],1694年6月4日—1774年12月16日),法国经济学家,重农主义的领袖、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先驱。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1]。
魁奈早年以行医为生,后在任路易十五宫廷御医时开始研究经济学。
1758年魁奈写出著名的《经济表》,他用图表来说明社会各经济阶级和部门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它们之间支付的流通,并提出了经济平衡的假说。
他提倡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该思想——甚或名字——很可能来自中国无为哲学的启发[2][3])。
魁奈对中国的经济有所研究,曾著有《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
魁奈更提出“纯产品学说”,他认为物质才是财富,唯有农业才能使财富增加,而工业只能改变财富的形态,不能增加财富的数量,服务业更不能增加财富的数量。并进一步提出“土地单一税理论”,也就是说既然农业创造出纯产品,所以他主张只对土地的收入征缴税收。
后来的李克洲认为,魁奈的经济思想,来源于他所处的时代。为此,李克洲对魁奈提出“纯产品学说”的解释为:“魁奈时代的法国,农业中已经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在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发展起来,还是由小业主性质的生产经营占据主导地位。”
可见因为魁奈所处的农业社会环境,当时的确存在“纯产品”(利润)这种现象,但是在工业社会中,这种观念就不存在了。
因此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在重农学派本身得出的结论中,对土地所有权的表面上的推崇,也就变成了对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上的否定和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肯定”。
因此,在农业中,存在“纯产品”(利润),而在工业中,就不存在“纯产品”(利润)。但魁奈由于没有所有权决定价值的思想,因此他错误地认为,“纯产品”来自自然的恩惠。
虽然时空背景如此,但是他很得亚当斯密的尊重。
亚当斯密曾在1764年至1766年间和他的弟子一同游览欧洲,大多是在法国,在那里斯密也认识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英。
魁奈身为重农主义学派的领导人,斯密极为尊重他的理论。但是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一书,就否定了重农主义学派对于土地的重视,相反的,斯密认为劳动才是最重要的,而劳动分工将能大量的提升生产效率。
参考文献
Derk Bodde. CHINESE IDEAS IN THE WEST (PDF). ASIAN TOPICS IN WORLD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2005 [2015-04-08].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4-10-09).
1 Source (PDF). [2008-03-04].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08-03-07).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John M. Hobson, p.196
附录François Quesnay
François Quesnay (French: [fʁɑ̃swa kɛnɛ]; 4 June 1694 – 16 December 1774) was a French economist and physician of the Physiocratic school.[1] He is known for publishing the "Tableau économique" (Economic Table) in 1758, which provide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ideas of the Physiocrats.[2] This was perhaps the first work attempting to describe the workings of the economy in an analytical way, and as such can be viewed as one of the fir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thought. His Le Despotisme de la Chine, written in 1767, describes Chinese politics and society, and his own political support for enlightened despotism.[3]
Life
Quesnay was born at Méré near Versailles, the son of an advocate and small landed proprietor. Apprenticed at the age of sixteen to a surgeon, he soon went to Paris, studied medicine and surgery there, and, having qualified as a master-surgeon, settled down to practice at Mantes. In 1737 he was appointed perpetual secretary of the academy of surgery founded by François Gigot de la Peyronie, and became surgeon in ordinary to King Louis XV. In 1744 he graduated as a doctor of medicine; he became the physician in ordinary to the king, and afterwards his first consulting physician, and was installed in the Palace of Versailles. His apartments were on the entresol, whence the Réunions de l'entresol[clarification needed] received their name. Louis XV esteemed Quesnay highly, and used to call him his thinker. When he ennobled him he gave him for arms three flowers of the pansy[4] (derived from pensée, in French meaning thought), with the Latin motto Propter cogitationem mentis.[5]
He now devoted himself principally to economic studies, taking no part in the court intrigues which were perpetually going on around him. Around 1750 he became acquainted with Jacques C. M. V. de Gournay (1712–1759), who was also an earnest inquirer in the economic field; and round these two distinguished men was gradually formed the philosophic sect of the Économistes, or, as for distinction's sake they were afterwards called, the Physiocrates. The most remarkable men in this group of disciples were the elder Mirabeau (author of L'Ami des hommes, 1756–60, and Philosophie rurale, 1763), Nicolas Baudeau (Introduction a la philosophie économique, 1771), Guillaume-François Le Trosne (De l'ordre social, 1777), André Morellet (best known by his controversy with Galiani on the freedom of the grain trade during the Flour War), Lemercier de La Rivière, and du Pont de Nemours. Adam Smith, during his stay on the continent with the young Duke of Buccleuch in 1764–1766, spent some time in Paris, where he made the acquaintance of Quesnay and some of his followers; he paid a high tribute to their scientific services in his Wealth of Nations.[6][4]
Quesnay was married in 1718 to a woman named Marianne Woodsen, and had a son and a daughter; his grandson by the former was a member of the first Legislative Assembly. He died on 16 December 1774, having lived long enough to see his great pupil, 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Baron de Laune, in office as minister of finance.[4]
Works
His economic writings are collected in the 2nd vol. of the Principaux économistes, published by Guillaumin, Paris, with preface and notes by Eugène Daire; also his Oeuvres économiques et philosophiques were collec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 by August Oncken (Frankfort, 1888); a facsimile reprint of the Tableau économique, from the original MS., was published by the British Economic Association (London, 1895). His other writings were the article "Évidence" in the Encyclopédie, and Recherches sur l'évidence des vérites geometriques, with a Projet de nouveaux éléments de géometrie, 1773. Quesnay's Eloge was pronounced in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by Grandjean de Fouchy (see the Recueil of that Academy, 1774, p. 134). See also F.J. Marmontel, Mémoires; Mémoires de Mme. du Hausset; H. Higgs, The Physiocrats (London, 1897).[4]
Economics
In 1758 he published the Tableau économique (Economic Table), which provide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ideas of the Physiocrats. This was perhaps the first work to attempt to describe the workings of the economy in an analytical way, and as such can be viewed as one of the fir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thought.[7]
The publications in which Quesnay expounded his system were the following: two articles, on "Fermiers" (Farmers) and on "Grains", in the Encyclopédie of Diderot and Jean le Rond d'Alembert (1756, 1757);[8][4] a discourse on the law of nature in the Physiocratie of Dupont de Nemours (1768); Maximes générales de gouvernement economique d'un royaume agricole (1758), and the simultaneously published Tableau économique avec son explication, ou extrait des économies royales de Sully (with the celebrated motto, Pauvres paysans, pauvre royaume; pauvre royaume, pauvre roi); Dialogue sur le commerce et les travaux des artisans; and other minor pieces.[4]
The Tableau économique, though on account of its dryness and abstract form it met with little general favor, may be considered the principal manifesto of the school. It was regarded by the followers of Quesnay as entitled to a place amongst the foremost products of human wisdom, and is named by the elder Mirabeau, in a passage quoted by Adam Smith,[6] as one of the three great inventions which have contributed most to the stability of political societies, the other two being those of writing and of money. Its object was to exhibit by means of certain formulas the way in which the products of agriculture, which is the only source of wealth, would in a state of perfect liberty be distributed among the several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namely, the productive classes of the proprietors and cultivators of land, and the unproductive class composed of manufacturers and merchants), and to represent by other formulas the modes of distribution which take place under systems of Governmental restraint and regulation, with the evil results arising to the whole society from different degrees of such violations of the natural order. It follows from Quesnay's theoretic views that the one thing deserving the solicitude of the practical economist and the statesman is the increase of the net product; and he infers also what Smith afterwards affirmed, on not quite the same ground, that the interest of the landowner is strictly and indissolubly connected with the general interest of the society. A small edition de luxe of this work, with other pieces, was printed in 1758 in the Palace of Versailles under the king's immediate supervision, some of the sheets, it is said, having been pulled by the royal hand. Already in 1767 the book had disappeared from circulation, and no copy of it is now procurable; but, the substance of it has been preserved in the Ami des hommes of Mirabeau, and the Physiocratie of Dupont de Nemours.[4]
Orientalism and China
Quesnay is known for his writings on Chinese politics and society. His book Le Despotisme de la Chine, written in 1767, describes his views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system.[3] He was supportive of the meritocratic concept of giving scholars political power, without the cumbersome aristocracy that characterized French politics, and the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e to the welfare of a nation. Gregory Blue writes that Quesnay "praised China as a constitutional despotism and openly advocated the adoption of Chinese institutions, including a standardized system of taxation and universal education." Blue speculates that this may have influenced the 1793 establishment of the Permanent Settlement in Bengal by the British Empire.[9] Quesnay's interests in Orientalism has also been a source of criticism. Carol Blum, in her book Strength in Numbers on 18th century France, labels Quesnay an "apologist for Oriental despotism."[10]
Because of his admiration of Confucianism, Quesnay's followers bestowed him with the title "Confucius of Europe."[11] Quesnay's infatuation for Chinese culture, as described by Jesuits, led him to persuade the son of Louis XV to mirror the "plowing of sacred land" by the Chinese emperor to symbolize the link between government and agriculture.[12]
On Taxation
Quesnay acknowledged three economic classes in France: the "proprietary" class consisting of only landowners, the "productive" class of agricultural workers, and the "sterile" class of merchants. Quesnay saw no benefit to the sterile class and believed the productive to be all important. Quesnay viewed France's agriculture as backward and unproductive compared to Britain during the time he was residing in the Palace of Versailles [13] . Despite residing in the Palace, Quesnay believed agriculture was the heart of the economy and of special importance to him. Quesnay argued that taxes placed on cultivators are only harmful to society as these taxes will reduce the incentive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axing proprietors (property holders) does not destroy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meaning there is no decline in output. Quesnay wanted proprietors to bear the full burden of the tax in the country as taxing cultivators is a negative consequence for everyone. Removing incentive from cultivators reduce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agricultural surplus Quesnay believed to be the heart of the economy [14]. Quesnay also opposed indirect taxes in contrast to direct taxes. These "indirect taxes" are placed on the French public by proprietors whose greed demands immunity from taxation. Direct taxes on proprietors has no impact on reproduction and economic decline [14]. Reducing indirect taxes and increasing direct taxes gives the French a surplus of agriculture and the funding the country needs. However, this opinion was not very popular among the wealthy of which Quesnay spent time regularly with. He spent some of his time fearing for his life in the Palace.
See also
Contributions to liberal theory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Liberalism
Ronald L. Meek
Circular flow of income
Notes
Cutler J. Cleveland, "Biophysical economics", Encyclopedia of Earth, Last updated: 14 September 2006.
See the biographical note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Volume 31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89) p. 605.
Ina Baghdiantz McCabe (15 July 2008). Orientalism in Early Modern France: Eurasian Trade, Exoticism and the Ancien Regime. Berg Publishers. pp. 271–72. ISBN 978-1-84520-374-0.
One or more of the preceding sentences incorporates text from a publication now in the public domain: Chisholm, Hugh, ed. (1911). "Quesnay, François".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Vol. 22 (11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742–743.
"Nouvelles Ephemerides, Économiques, Seconde Partie, Analyses, Et Critiques Raisonnées. N° Premier. Éloge Historique De M. Quesnay, Contenant L'Analyse De Ses Ouvrages, Par M. Le Cte D'A***". Taieb.net. Retrieved 16 August 2012.
Smith, Adam, 1937, The Wealth of Nations, N. Y.: Random House, p. 643; first published 1776. Phillip Anthony O'Hara (1999).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Economy. Psychology Press. p. 848. ISBN 978-0-415-18718-3. Retrieved 21 July 2012.
Kafker, Frank A.; Chouillet, Jacques (1990). "Kafker, Frank A.: Notices sur les auteurs des 17 volumes de « discours » de l'Encyclopédie (suite et fin). Recherches sur Diderot et sur l'Encyclopédie Année (1990) Volume 8 Numéro 8 p. 112". Recherches Sur Diderot et Sur l'Encyclopédie. 8 (1): 101–121.
E. S. Shaffer (30 November 2000). Comparative Criticism: Volume 22, East and Wes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39–40. ISBN 978-0-521-79072-7.
Carol Blum (5 February 2002). Strength in Numbers: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and Power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JHU Press. p. 16. ISBN 978-0-8018-6810-8.
Murray N. Rothbard (2006).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Adam Smith.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p. 366. ISBN 978-0-945466-48-2.
Geoffrey C. Gunn (2003). First Globalization: The Eurasian Exchange, 1500 to 1800. Rowman & Littlefield. p. 148. ISBN 978-0-7425-2662-4.
附录:科斯定理
知乎回答
作者:SilliySeal
科斯定理:只要产权明确,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则不管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
举个例子,有个村子在河流下游,造纸厂在河流上游,村子抱怨造纸厂污染河流,造纸厂认为河流没有归属,但谁都不愿意去买一套污水处理设备,这样僵持不下。
因为科斯定理,将河流归属给造纸厂,村民没办法只能自己掏钱装污水处理设备,这样造纸厂可以排污水,村民也不必收到污水的影响,结果是有效率的。
如果将河流归给村民,那么村民就有权利要求造纸厂要么停工要么掏钱安装污水处理设备,污水厂没办法只能装了,这样最后结果又达到了奇妙的平衡。
维基百科词条
科斯定理(英语:Coase theorem),描叙一个经济体系内部的资源配置与产出,在外部性存在的情形下,其经济效率所可能受到的影响。这个理论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1960年代的论文中提出。乔治·斯蒂格勒在1966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首次将他的见解进行归纳,并被后人称为科斯定理,事实上他不曾使用过科斯定理一词,或者定义他们可以自己解决外部性问题。
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中由罗伯特·库特对“科斯定理”的解释。他写道:“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以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
科斯是在考虑无线电广播频率时发展出科斯定理的。两家广播电台假如在同一个频段广播,便可能互相干扰,而管理者则必须将各个频段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分配给不同的广播电台,从而消除电台之间的干扰。科斯的定理认为,只要对频率的产权界定清楚,那么无论频率在初始阶段如何分配,市场最终都会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过程如下:在两家存在争议的电台之间,从争议频段中可以获得更大利益的电台甲假如对该频段没有产权,他也有足够的诱因向另一家电台乙购买或租用该频段的使用权,因为甲为了拿到频段而愿意付出的金额必定大于乙为了放弃频段而愿意接受的金额。因此,频段的初始分配会影响到两家电台的盈亏状况,却改变不了频段达到最有效率的分配状态的必然结果。
以上的情况,只有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才成立,而在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易中便会出现阻碍。比如在以上的例子当中,甲为了拿到频段而愿意出的金额当中,有一部分必须作为甲乙双方的交易成本(如谈判费、诉讼费等)被扣除,余下的数量或许就不足以为了放弃频段而愿意接受的金额,甲可能就争取不到对该频段的使用权,市场就无法达到最有效率的状况。因此,在分配产权时,分配者应该尽量减低有可能出现的交易成本,使市场参与者能够进行交易,这样市场才能够达到有效率的最终状态。
附录:外部性
在经济学中,外部性(英语:externality)或外部成本(英语:external cost)、外部效应、溢出效应,是作为另一方(或多方)活动的影响而产生的未参与第三方的间接成本或收益。 外部性可被视为涉及消费者或生产者市场交易的未定价商品。 车辆废气造成的空气污染就是一个例子。 空气污染给社会造成的代价,不是由车辆生产者或使用者向社会其他人支付的。 来自工厂的水污染是另一个例子。 所有消费者都因污染而变得更糟,但市场并没有为这种损害提供补偿。 正外部性是指个人在市场上的消费增加了他人的福祉,但个人不向第三方收取收益。 第三方本质上是获得免费产品。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可能是面包店上方的公寓,每天早上都能闻到新鲜糕点的香味。 住在公寓里的人不会为此利益补偿面包店。
外部性的概念最早是由经济学家亚瑟·塞西尔·庇古在 1920 年代提出。负外部性的典型例子是环境污染。 庇古认为,对负外部性征收等于边际损害或边际外部成本的税(后来称为“庇古税”)可用于将其发生率降低到有效水平。 随后的思想家们争论了是征税还是监管负外部性更可取、庇古税收的最佳效率水平,以及什么因素导致或加剧了负外部性,例如为公司投资者提供有限责任公司所造成的损害。
当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或消费的私人价格均衡无法反映该产品或服务对整个社会的真实成本或收益时,通常会出现外部性。这导致外部性竞争均衡不遵守帕累托效率条件。 因此,由于可以更好地分配资源,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一个例子。
外部性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 政府和机构经常采取行动将外部性内部化,因此市场定价交易可以包含与经济主体之间交易相关的所有收益和成本。最常见的做法是对这种外部性的生产者征税。 这通常类似于不征税的报价,一旦外部性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征收非常高的税。 然而,由于监管机构并不总是掌握有关外部性的所有信息(参考信息不对称),因此可能难以征收正确的税款。 一旦外部性通过征税被内部化,竞争均衡理论上会达到帕累托效率。
例如,造成空气污染的工厂制造活动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健康和清洁成本,而选择对房屋进行防火处理的个人的邻居可能会受益于降低火势蔓延到自己房屋的风险。 如果存在外部成本,例如污染,生产者可能会选择生产比要求生产者支付所有相关环境成本时生产的更多的产品。 由于自主行为的责任或后果部分在自身之外,因此涉及成本外部化(英语:Cost externalizing)因素。 如果存在外部利益,例如公共安全,则生产的商品数量可能少于生产者因他人的外部利益而获得回报的情况。 同时,从社会经济学的观点来看:
- 个人通常会倾向于“外部不经济”的消费行为,因为有害外部性商品带来的成本不需要个人承担(如污染),经济上称此为“过度消费”(英语:overconsumption)
- 而由于有益外部性商品带来的收益并不能被个人独占,个人通常在一定程度上不愿意做出“外部经济”的消费行为(如教育),经济上称此为“不充分消费”(英语:underconsumption)。
外部效应是经济决策的不平衡影响,不能归咎于决策者,因为决策者与受决策影响者之间缺乏价格或市场机制调和其利益。
一桩交易的买方或卖方如果认为结果对自己不利,那么交易不会成功,所以两愿交易被认为是对于双方都有利的;但是交易成果可能会对第三方造成额外的影响。从受到影响的第三方角度来看,这些影响可能是负面的(例如工厂排放污染),也有可能是正面的(采蜜的蜂群也会附带给邻近植物授粉)。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认为在合理条件下,外部性的存在将导致非社会最优的结果。那些遭受外部成本的人是不由自主的,而那些享受外部利益的人则不需耗费成本。
如果有外部成本存在,两愿交易可能会减少社会福利。遭受空气污染外部性影响的人将其视为自己的效用降低:主观的生气不满或自己负担的成本,例如医疗费用较高。外部性甚至可被视为危害居民的肺部,侵犯到他们的生命与财产权。因此,外部成本可能构成道德或政治上的问题;或被视为生命与财产权无法明确界定的情况,例如,排放污染到物权没有归属人的水域(象征性地为社会大众公有,或是明文在某些国家或/且法定传统上;例如禁止排放污水到溪流或海洋中)。
另一方面,正面的外部性将会增加第三方的效用,集体社会福利得到改善;而提供此外部性的私有者却无法获取其利益,即少有意愿增多生产;那么依无政府的理论模式中,集体的福利不会达到社会最优的数量。具有正面外部性的物品包括教育(被认为可提高社会的生产力和福利,尽管更高教育水平的外部性,将由更高工资率而内部化),公共卫生计划(可降低第三方的健康风险和成本,例如传染疾病)和正直的司法与执法。
正面的外部性通常与搭便车问题有关。例如,接种疫苗的人减少了周围其他人感染相关疾病的风险;在高水平的防疫措施下,社会将获得很大的健康福祉; 但任何人都有可能拒绝接种疫苗,却仍然借由“搭便车”的方式,规避掉原应支付接种疫苗的费用。
当涉及负面的外部性时,有一些提高整体社会效用的理论方法。其一是以市场驱动来纠正负面外部成本,对第三方不愿承担的成本将其“内部化”,例如要求污染者赔偿或修复排污所造成的任何损害。但在许多情况下,内部化成本或收益是不可行的,特别是无法确定造成外部性真正的货币价值。
尽管外部性不一定是轻微或局部的,自由贸易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有时将外部性称为“邻域效应”或“溢出效应”。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同样认为,外部性是因为拥有“个人财产权的明确定义”。
第2章 管理的专横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关税和对国际贸易的其他限制时,写道:
”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产业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向他们购买。“ ”在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而且必然在于,向售价最廉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这个命题是非常明白的,费心思去证明它,倒是一种滑稽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自私自利的诡辩混淆了人们的常识,这亦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在这一点上,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正相反。”
斯密的这些话,现在仍然同当时一样正确。在国内和国外的贸易中,从售价最低的地方购买物品而向出价最高的地方出售物品,是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的。然而“自私自利的诡辩”却导致出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使我们买卖什么、向谁买卖、以什么条件买卖、雇用谁或为谁工作、住在哪里以及吃什么、喝什么,总之,所有的一切都受到了限制。
亚当·斯密指责“商人和制造业者进行自私自利的诡辩”。在他那个时代,商人和制造业者可能是主要的罪人。现在他们有了许多同伙。的确,我们中间几乎没有哪个人不在这一或那一领域进行“自私自利的诡辩”。用波哥的不朽名言来说:“我们碰到了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责备“特殊利益”,但当“特殊利益”关系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就不责备了。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对自己有利的,对国家也有利——因而,我们的“特殊利益”便各不相同。
其最后结果是,各种约束和限制一起向我们涌来,使我们大家的处境如此之糟,以至如果取消所有这些限制,我们的处境反倒会好一些。为别人的“特殊利益”服务的措施给我们带来的损失远远大于为我们“特殊利益”服务的措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最明白的例子是国际贸易。某些生产者因关税或其他限制所得到的好处,抵不上给其他生产者尤其是一般消费大众造成的损失。自由贸易不仅能促进我们的物质福利,而且还能促进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协调,鼓励国内的竞争。
【按:政府决策要以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福利为依据。】
控制对外贸易会发展成控制国内贸易。它们会同经济活动的各方面交错在一起。这种控制经常受到辩护,认为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特别是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更是这样。把1867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同1947年独立后的印度作一比较,我们就能检验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和其他例子一样,这一比较说明,国内外的自由贸易是贫穷国家改善其人民生活的最好途径。
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经济控制,不仅限制了我们利用经济资源的自由,而且也影响了我们在言论、出版和信仰等方面的自由。
国际贸易
人们常说,如果经济学家意见不一致,那就一定是坏的经济政策;相反,如果所有经济学家意见一致,那就一定是好的经济政策。经济学家确实时常意见不一,但就国际贸易来说,情况却不是这样。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不管在其他问题上思想立场如何,在国际贸易这一问题上却几乎一致认为,自由贸易最符合各贸易国和整个世界的利益。可是各国都征收关税。仅有的几个较为重要的例外是:1846年废除谷物法后英国将近一个世纪的自由贸易、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三十年的自由贸易和今天香港的自由贸易。美国在整个十九世纪一直征收关税,二十世纪,特别是1930年国会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后,美国进一步提高了关税。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法案加重了大萧条的严重程度。自那时以来,通过签订一系列国际协议,关税有所削减,但目前仍然很高,也许高于十九世纪的水平。由于国际贸易中的项目种类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现在无法作精确的比较。
同以往一样,现在仍有许多人支持征收关税,并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国内工业。钢铁生产者和钢铁工人工会要求限制从日本进口钢材。电视机生产者及工会则疏通国会议员,试图用“自动协议”的办法限制从日本、台湾或香港进口电视机和电视机零件。纺织品制造商、鞋类制造商、养牛业者、制糖业者和无数其他的人也都抱怨受到了来自外国的“不公平的”竞争,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他们。当然,没有哪一个集团在赤裸裸的自我利益的基础上提出这种要求。每个集团都讲“总的利益”,讲维持就业或加强国家安全的必要性。近来,在这些传统的主张限制进口的理由之外,又增加了另外一条理由,就是需要加强美元对马克或日元的地位。
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理由
历来很少听到的是消费者的呼声。近年来,所谓消费者特殊利益集团越来越多。但是,任你查遍报章杂志或是国会作证记录,也找不到任何记载,表明他们发起过对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的集中攻击,尽管消费者是这种限制的主要受害者。我们将在第七章里看到,那些自称为消费者说话的人,关心的是别的事情。
个别消费者的呼声,在工商业者及其雇员的一片“自私自利的诡辩”的吵嚷声中被淹没了。结果是把问题严重歪曲了。例如,主张征收关税的人认为,创造就业机会本身就是一个可取的目标,不管受雇者干些什么,而且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我们需要的只是工作,我们可以创造任何数目的工作——例如,让人挖坑再填上,或者做其他无用的事。工作有时候自身就是酬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我们为取得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付出的代价。我们真正的目的不光是要有工作,而且要有生产性的工作——那些意味着将有更多的货物和劳务供消费的工作。
另外一个很少受到驳斥的谬论是,出口好,进口不好。实际远非如此。我们并不能吃、穿或享受输出的货物。相反,我们可以吃中美洲的香蕉,穿意大利的鞋,开德国的车,并在日本产的电视机上欣赏节目。我们从对外贸易中得益的是输入。出口是我们为进口付出的代价。正如亚当·斯密非常清楚地看到的那样: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能为出口换回尽可能多的进口,或者为进口支付尽可能少的出口,那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我们所使用的使人产生误解的字眼,反映了我们的一些概念性错误。“保护”实际上意味着剥削消费者。“贸易顺差”的实际意义是出口超过进口,也就是说输出货物的总值超过输入货物的总值。在自己家里,你一定愿意少付多得,而不是相反,可是在对外贸易中,这却被称作“收支逆差”。
支持关税的一个最得人心的论据,是所谓需要保护美国工人的高生活水平,使之免遭日本、韩国或香港的工人的“不公平的”竞争,因为这些工人愿意为低得多的工资工作。这个论据错在哪里,难道我们不想保护我国人民的高生活水平吗?
这个论据的错误,在于滥用“高”工资和“低”工资这些字眼。高工资和低工资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美国工人得到的是美元;日本工人得到的是日元。怎么比较以美元支付的工资和以日元支付的工资呢?一美元合多少日元,它们之间的汇率由什么来决定?
让我们来看下面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况。先假设一美元合三百六十日元。这是多年间的实际汇率。按这个汇率,假定日本人能够比我们在美国花比较少的美元生产和销售各种东西——电视机、汽车、钢铁以至大豆、小麦、牛奶和冰淇淋。如果实行国际自由贸易,我们将试图从日本购买我们的所有货物。也许这就是为关税辩护的人们所描绘的那种极端可怕的情景——日本货泛滥成灾而我们什么也卖不出去。
在吓得不知所措以前,先来进一步分析一下。我们怎样来偿付日本人呢?我们将给他们美钞。他们拿了这些钞票将干什么,我们上面假定,按三百六十日元对一美元的汇率,什么东西都是在日本便宜,因此在美国市场上,没有任何东西是他们想买的。如果日本出口商愿意把美钞烧了或是埋了,那于我们就太好了。我们可以用这些能够大量地很便宜地制造出来的绿票子换得各种货物。我们将有一种能够想得出来的最了不起的出口工业。
自然,日本人事实上不会把有用的货物卖给我们,换取无用的票子去烧掉或埋掉。他们同我们一样,想为他们的工作得到一些实在的报酬。如果按三百六十对一的汇率,所有的货物在日本比在美国便宜,出口商将试图卖出他们手中的美元,将试图按三百六十对一的比价卖掉它们,以购买便宜的日本货。但是谁愿意收购美元呢,不仅日本出口商想卖掉美元,日本的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如果三百六十日元能够在日本比一美元在美国多买到每一种东西的话,那么,没有一个人会愿意拿三百六十日元换一美元。出口商发现没有人愿意按三百六十对一的比价买进美元,就会少要一些日元。于是美元的日元牌价就会下跌——跌至三百比一,或二百五十乃至二百比一。反过来说,要购买一定数量的日元,需付越来越多的美元。日本货是以日元标价的,所以它们的美元标价会涨。反之,美国货是以美元标价的,因此,日本人用一定数额的日元得到的美元越多,对日本人来说,美国货的日元标价就越便宜。
美元的日元标价,将一直下跌到日本人从美国购买的货物的美元价格基本上等于美国从日本购买这些货物的美元价格为止。按那个价格,每个想用美元购买日元的人,都会找到愿意卖出日元换取美元的人。
自然,实际情况要比这个假设的例子复杂。参加贸易的是许多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和日本,而且贸易常采取迂回的方式。日本人可能把他们赚得的一些美元花在巴西,巴西人又把它用在德国,德国人又花在美国,总之,实际情况无比错综复杂。但原则是一样的。不管在哪个国家,人们要美元总是为了购买有用的东西,而不是为了囤积。
另外一个复杂情况是,美元和日元并不只是用于购买货物和劳务,还用来投资和送礼。整个十九世纪,美国几乎每年都有国际收支逆差,但这种贸易逆差却给每个人带来了好处。外国人想在美国投资。例如英国愿意向我们输出货物,以换取纸片——不是美钞,而是些保证过些日子连本带利偿还借款的债券。英国人愿意送货物给我们,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债券是好的投资。一般说来,他们是对的。因为同其他方法相比,他们从这种积蓄中得到的报酬比较高。而我们也得到了好处,外国投资使我们能够比完全依靠自己的积蓄发展得更快。
二十世纪,情况发生了逆转。美国的公民发现,他们向外国投资可以得到比在国内投资更高的报酬。结果,美国把货物送出国外,换取债务凭证,即债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以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援助计划的形式给外国送礼。我们把货物和劳务送给外国,以表示我们确实是在促进世界的和平。除政府的馈赠外,还有私人的礼物,如慈善团体开展的活动、教会资助的传教活动、个人对国外亲戚朋友的资助等。
这些复杂情况并不改变上述假设的极端情况所说明的结论。在现实世界里,象在假想的那个世界里一样,只要美元的日元标价或马克标价或法郎标价是在自由市场上由自愿的交易决定的,就不会发生收支差额的问题。说美国高工资工人作为一个整体会受到外国低工资工人的“不公平的”竞争,这话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自然,某一部分工人可能因为国外制造出了新产品或改进了产品或是外国生产者能够更便宜地生产某些产品,而受到损害。但这同其他美国公司制造出了新产品或改进了产品或是发现了更节省成本的生产方法而给某一部分工人带来的影响,并无区别。实际上这就是市场竞争,正是依赖于市场竞争,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才得以提高的。我们若想从一种生气蓬勃的、充满活力的、富于创造性的经济制度中得到好处,就必须认识到运动和调整的必要性。使这种调整进行得轻松些,也许是可取的,我们为此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例如实行失业保险等。但我们在努力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不应破坏制度的适应性。破坏制度的适应性,无异于杀鸡取蛋,自绝生财之道。不论我们做什么,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对国内外贸易一视同仁。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开展对外贸易有利可图?当前美国工人的生产率要高于日本工人的生产率。究竟高多少难以确定,每人的估计不一样。我们暂且假设高一半。那么平均说来,美国工人的工资可以买到的东西就应该是日本工人的一倍半。让美国工人来做任何事情,如果效率达不到日本工人的一倍半,就是浪费。用一百五十多年前创造的经济行话来说,这就是所谓相对有利条件原则。即使我们生产每种东西都比日本人更有效率,我们也不应样样都生产,这样做是不上算的。我们应当集中搞那些我们最内行的事,那些最能发挥我们优越性的事。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位律师会打字,比他的秘书快一倍,他就应当把这个秘书解雇而自己打字吗?如果这位律师打字比他的秘书强一倍,而干律师工作强五倍,那么他搞法律事务,让秘书去打字,他们的生活都会过得更好。
另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的根源据说是外国政府向它们的生产者提供补贴,使他们能够在美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假定一个外国政府提供这样的补贴(无疑,有些政府正是这样做的),受损失的是谁,得好处的又是谁,外国政府为了提供补贴,就得向公民征税。出钱补贴的是这些公民,得益的是美国消费者。他们得到便宜的电视机或汽车或是别的什么得到补贴的东西。我们应该抱怨这种反过来的外国援助计划吗,我们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或后来的援外计划把货物和劳务送给别国作为礼物是高尚的,难道外国以低于成本的价钱把货物和劳务卖给我们,以这种间接形式送礼就不光彩了吗?倒是外国公民应该抱怨。为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和本国受到补贴的工业的业主和工人的利益,他们必须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无疑,如果外国政府突如其来地或毫无一定规律地提供补贴,会给美国国内生产同样产品的工业的业主和工人造成不良影响。然而这是做生意通常要冒的危险。企业决不会抱怨使它发横财的不平常事件或意外事件。自由企业制度就是一个赢利和赔钱的制度。正如前面指出过的,任何用来缓和调整以适应突然变化的措施,都应该对国内和国外贸易一视同仁。
总之,混乱很可能是暂时的。假定由于某种原因,日本决定大量补贴钢铁工业。如果不增加关税或施行限额,输入美国的钢铁会急剧增加。这将使美国国内的钢铁价格下跌,迫使钢铁生产者减产,造成钢铁业的失业。另一个方面,钢铁制品的价格则可能下降。买这些产品的人将有多余的钱可用来买别的东西。对其他东西的需求会增加,生产这些东西的企业的就业人数也会增加。自然,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吸收现在失业的钢铁工人。但是其他工业里原来失业的工人将有工可作,能抵消这种影响。总的就业人数不一定会减少,而由于钢铁业不再需要的工人可以用来生产别的东西,生产将会增加。
这种由于片面地看问题而产生的谬见,同样表现在有些人为了增加就业而要求征收关税的行动上。譬如说对纺织品征收关税,国内纺织业的就业和产量会增加。但是,外国生产者不能在美国出售他们的纺织品,他们赚得的美元就会减少。赚得的美元减少,他们能花在美国的钱也就随之减少。因而进口减少多少,出口也会减少多少。纺织业的就业人数会增加,但出口工业的就业人数会减少。而工人转移到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去,会使总产量减少。
说国内钢铁业兴旺是国防所必需,这种国家安全论也没有更多根据。国防的需要只占用美国国内用钢量的一少部分。而且不可想象,钢铁的完全自由的贸易会毁掉美国的钢铁业。由于接近材料和燃料的来源,接近市场,只会有利于保障国内相对巨大的钢铁工业。的确,由于需要应付外国的竞争而不是受到政府的壁垒的掩护,很可能造就一个比我们现有的更为强大和有效的钢铁业。
【按:提高钢铁行业的反脆弱性,降低钢铁行业的垄断程度。】
假定那不可能发生的事果真发生了,假定确实到国外去买全部我们需用的钢更来得便宜。也还有其他办法确保国家安全。我们可以囤储钢铁。这很容易,因为钢铁占地方较少而且不会腐烂。我们可以封存一些钢厂,就象封存船只一样,需要时再启用。无疑还可以有别的办法。钢铁公司在新建一座钢厂以前,先研究几种不同的方案,以选择最优、最经济的厂址,然而钢铁业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提出那么些补贴的要求,却从未说明采用其他方法来保障国家安全要花费多少。除非他们能说明,我们可以肯定国家安全论是工业的自我利益的饰词,而不是补贴的正当理由。
无疑,钢铁业的经理们和钢铁工人工会人员提出国家安全的论据是真诚的。真诚这种德性被估价得太高了。我们都能够说服我们自己,相信对我们好的对国家也好。我们不应当埋怨钢铁生产者提出这种论点,而应怪我们自己相信了它。
说我们必须保卫美元,我们必须不让它同其他货币——日元、西德马克或瑞士法郎——的比价跌落,这个论点怎么样?这完全是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问题。如果外汇率是在自由市场上决定,它就会定在收盘时的比率。这样产生的美元对譬如说日元的比价,可能暂时跌到合理的水平以下,低于按美元算的美国货和按日元算的日本货的相对成本。要是这样,这就会给予注意到这个情况的人一种刺激去买进美元,留存一些时候,等其比价上升来获利。由于降低了出口到日本的美国货的日元价格,就会刺激美国出口;由于抬高了日本货的美元价格,就会减少从日本的进口。这些发展会增加对美元的需求而纠正开始时过低的比价。美元的价格,如果是自由确定的话,就同所有其他的价格一样,起同样的作用。它传递情报,提供促使根据情报采取行动的刺激,因为它影响进入市场的人的收入。
那为什么对美元的“疲软”生那么大气?为什么反复发生外汇危机?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外汇兑换率不是在自由市场上决定的。各国政府的中央银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来影响其货币的价格,在这一过程中,它们损失了它们公民们的巨额的钱(就美国来说,从1973年到1979年初,损失了将近二十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它们阻止了这一套重要的价格起其应有的作用。它们并没有能够阻止基本的经济因素对汇率最后产生影响,但却能够使人为的汇率维持很长时间。其后果是妨碍了适应基本因素的逐渐的调整。小的混乱累积成了大的混乱,最后发生一场严重的外汇“危机”。
为什么政府要干预外汇市场,因为汇率反映国内政策。美元比日元、西德马克和瑞士法郎弱,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比其他国家高得多。通货膨胀意味美元在国内能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少。它在国外能购买的东西也少了,这有什么奇怪呢,日本人、德国人或瑞士人不愿意按从前的比价兑换美元,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但政府也象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一样,总是费尽心机试图掩盖或抵消它们自己的政策造成的恶果。所以一个通货发得过多的政府就试图操纵汇率。当它失败的时候,就把国内通货膨胀归咎于汇率的下跌,而不承认正好相反的因果关系。
几世纪来,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各种论文书籍浩如烟海,主张征收关税的,只有三个论点在原则上还多少站得住脚。
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过的国家安全论。虽然这个论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征收某些特定关税的饰词而不是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有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确实需要维持一些不经济的生产设备。如果我们已不是在讨论理论上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在某种情况下确认为了加强国家安全有必要征收关税或对贸易实施其他限制,那就得比较一下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特定目标的代价,并确立至少表面上是确凿的证据,证明征收关税是代价最低的方法。但实际上却很少有人作这种比较。
第二个是“婴儿工业”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提出过这个论点。据说,有一种潜在的工业,一旦建立并在其痛苦的成长时期得到帮助,就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平等地进行竞争。据说,暂时征收关税是有道理的,是为了保护那处在襁褓中的潜在的工业,使它能长大成人,能自立地发展。即使那工业在建成后真正能成功地竞争,那也不能说明开始的时候征收关税是有道理的。就消费者来说,只是在一种情况下值得在开始时去补贴(他们用征收关税实际上做的事)那种工业,即他们往后通过某种方式,至少能收回补贴,例如使该工业产品的价格低于世界水平,或由于拥有这个工业而得到好处。但在这种情况下,补贴就是必需的吗,如果不提供补贴,最先进入那个工业的企业家开始时遭受的损失就真的得不到补偿了吗?归根结底,大多数公司在兴起时,头些年都要蚀本。它们进入一门新的工业是这样,进入一门已有的工业也是这样。也许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值得给予最初的投资,但最初的加入者遭受的损失却不能得到补偿。但推敲起来,其实并非如此。
婴儿工业论是一种烟幕。那所谓的婴儿老也长不大。一旦征收关税,就难再予以取消。而且,这个论点很少用来为真正还没有生下来的婴儿说话,这种婴儿要是能得到暂时的保护,本可以生下来并生存下去的。没有人为它们说话。这个论点用来主张征收关税,是为了那些颇上了些年纪的婴儿,他们已经能够施加政治压力了。
【按:需要关税保护的往往都是上了年纪的夕阳产业~。】
第三个不能立即排除的主张征收关税的论点是“以邻为壑”论。一个国家如果是一种产品的主要生产者,或者能够联合一些别的生产者一起控制大部分生产,可能利用它的卖主独家垄断地位抬高产品的价格(石油输出国组织就是当前的一个例子)。这个国家可以并不直接提价,而是间接地通过对产品征出口税——出口关税。它本身得到的好处可能抵不过其他国家的损失。但从本国的观点看,可以有所得。同样,一个国家如果是一种产品的主要购买者——用经济学行话来说就是拥有买主独家垄断力量——它可能通过同出售者讨价还价强使他们接受过低的价格,从中得到好处。一个办法就是对这种产品征收进口税。出售者净得的是减去了关税的价钱,这就是为什么征收进口税相当于以低价购买。事实上关税是外国人付的(我们想不出一个实在的例子)。实际上,这种民族主义的办法很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进行报复。此外,就婴儿工业论来说,实际的政治压力产生的关税结构,事实上既不利用卖主独家垄断地位,也不利用买主独家垄断地位。
第四个论点,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来而迄今被重复着的,是说自由贸易,要是所有其他国家都实行的话,会是件好事,但只要其他国家不实行自由贸易,美国也就无法实行自由贸易。这个论点,无论从原则上或在实践上都完全站不住脚。其他国家对国际贸易施加限制的确于我们有损,但那也损害它们自己。撇开上面谈过的三种情况不说,如果我们反过来也实施限制,我们只会给我们自己增加损失,也损害它们。竞相虐待绝不是处理敏感的国际经济政策的良方!这种报复行动不但不会使其他国家减少限制,相反,只会招致更多的限制。
我们是一个大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我们不应当要求香港、台湾规定纺织品的出口限额,以“保护”我们的纺织工业,而让美国的消费者和香港、台湾的中国工人吃亏。我们大谈自由贸易的好处,同时却运用政治经济力量使日本限制钢铁和电视机的出口。我们应当单方面走向自由贸易,不是一下子,而是经过一个时期,例如五年,按照事先宣布的速度进行。
很少有什么我们能够采取的措施,能比完全自由贸易更能促进国内和国外的和平事业。我们不应该以经济援助的名义赠款给外国政府,同时又对它们出产的东西施加限制,而应该采取一种一贯的和有原则的立场,因为赠款会促进社会主义,施加限制会妨碍自由企业的发展。我们可以告诉全世界:我们信仰自由并愿意实行。我们不能强迫你们实行自由。但我们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一切人提供充分的合作。我们的市场对你开放,没有关税或其他限制。你能够并愿意卖什么,就来这里卖好了,你能够并愿意买什么,就来这里买什么好了。这样,个人之间的合作就会成为世界范围的和自由的合作。
【按:“以经济援助的名义赠款给外国政府”往往是为了收买外国政府领导人特别是小致胜联盟的领导人。】
实行自由贸易的政治理由
相互依赖是当今世果上到处存在的特点;在经济领域本身,相互依赖存在于一套价格和另一套价格之间、一个工业和另一个工业之间、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之间。在更广泛的社会内,它存在于经济活动和文化、社会、慈善活动之间。在社会组织中,它存在于经济安排和政治安排之间、存在于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
在国际领域中也是一样,经济安排和政治安排交错在一起。国际自由贸易哺育不同文化和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正如国内自由贸易哺育不同信仰、态度和利益的个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一样。
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上,就如在任何国家的自由经济中一样,交易在私有的实体——个人、企业、慈善机构——之间进行。任何交易的条件,都由参加各方协议。除非各方都相信他们能从交易中得到好处,否则就做不成交易。结果,各个方面的利益取得了协调。普遍存在的是合作而不是冲突。
政府一插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一个国家里,企业从它们的政府那里谋求补贴,或者是直接的,或者以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的形式。它们将诉诸政治压力来使其他企业受到损失,规避威胁它们的利润以至生存的竞争者的经济压力。一国政府为了本国企业的利益进行干预,导致其他国家的企业向它们自己的政府寻求援助,来对抗外国政府采取的措施。私人之间的争议变成了政府之间的争议。每一次贸易谈判成了政治事件。政府高级官员乘坐喷气式飞机到世界各地去参加贸易会议。摩擦越来越大。各国人民对会议结果感到失望,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结果,普遍存在的是冲突而不是合作。
从滑铁卢到第一次世果大战的那一百年提供了一个显明的例子,说明自由贸易会对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多么良好的影响。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那一百年里,它实行了几乎完全自由的贸易政策。其他国家,尤其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各西方国家,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也许在形式上稍微有些不同。人们大体上都能按相互同意的条件,同任何人自由买卖,不管是住在哪里,住在同一个国家或不同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也许使我们在今天更感觉惊奇的是,人们可以自由地在整个欧洲旅行,或在世界大部分其他地方,不需要护照,也不受那重复的海关检查。他们可以自由移居,在世界大部分地方尤其是美国,可以自由入境并成为居民和公民。
结果,从滑铁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一百年,成了人类历史上西方国家之间最和平的时代。在这期间,只有过一些小战争,最著名的是克里米亚战争和普法战争。自然还有美国国内的大内战,它本身就是美国背离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而实行奴隶制的结果。
在现代世界上,关税和与此相类似的对贸易的其他限制,变成了国家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根源。但带来巨大麻烦的根源,却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当年的集体主义国家如希特勒的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佛朗哥的西班牙和现在的共产党国家如苏联及其卫星国和中国,都对经济进行干预。关税之类限制歪曲价格制度传递的信号,但至少还让个人有对这些信号作出反应的自由。集体主义的国家引入了影响深远的控制成分。
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公民同集体主义国家的公民之间,不可能进行完全的私人交易。有一方必定得由政府官员为代表。政治考虑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实行市场经济的政府容许其公民尽可能直接地同集体主义的政府作交易,摩擦可以减少。要想用贸易作为政治武器或用政治措施作为手段来增加同集体主义国家的贸易,那只会使不可避免的政治摩擦变得更厉害。
国际自由贸易和国内竞争
国内竞争的规模同国际贸易安排有密切关系。十九世纪后期,公众反对“托拉斯”和“垄断”的呼声导致建立了州际商业委员会并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这个法案后来受到许多其他立法行动的补充,来促进竞争。这些措施产生了很混杂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它们增加了竞争,但在另一些方面又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但是,即使这些措施完全达到其发起人的预想,也不能象取消国际贸易的一切限制那样,保证有效的竞争。在美国,虽然仅仅存在三大汽车生产者,而且其中之一已濒于破产,但这却对垄断价格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果让全世界的汽车生产者都来同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竞争美国的买主,那垄断价格的幽灵肯定会消失。
其他方面也是这样。没有政府以关税或其他办法公开和暗中的帮助,在一个国家里是很难确立垄断地位的。在世界范围,这更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德比尔公司对钻石的垄断,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看来成功的例子。我们不知道还有别的能没有政府的直接帮助而维持很久的垄断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早先的橡胶和咖啡卡特尔也许是受到政府帮助的最突出的例子。但是大多数这类由政府主持的卡特尔都维持不了多久。它们在国际的竞争压力下垮台了——我们相信石油输出国组织也会是这个下场。在一个实行自由贸易的世界上,国际卡特尔会更快消失。即使在贸易受到限制的世界上,美国也能够通过实行自由贸易(必要时单方面实行),来基本上消除国内的大垄断集团带来的威胁。
中央经济计划
在不发达国家旅行,我们一次又一次得到深刻的印象,那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所认为的事实同事实本身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异。
各地的知识分子都想当然地认为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是用来剥削人民大众的办法,而中央经济计划是未来的潮流,会把他们的国家推上迅速发展的道路。前不久,一位美国人批评印度的中央计划搞得过细,对此,一位很富有的而且文化修养极高的著名印度企业家——他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讽刺的那种大腹便便的资本家——进行了反驳。他明确告诉我们,象印度这样穷的国家的政府,只有控制进口、国内生产和收入的分配,也就是说,在所有这些使他发财致富的领域,授予他特权,才能保证社会的需要优先于个人的自私的需要。他只不过是重复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教授和知识分子的见解而已。
事实本身与这种见解大不相同。凡是个人自由的成分较大,普通公民的物质享受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增加,人们普遍对未来的发展抱有信心的地方,我们总是发现其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自由市场组织的。凡是国家严密控制其公民经济活动的地方,也就是说,凡是详细的中央经济计划统治一切的地方,那里的普通公民就受到政治的束缚,生活水平低下,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国家可能兴旺,可能开创不朽的功业,但普通公民成了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收入仅够维持他们适度的生产。
最明显的例子是东西德的对比。那本是一个整体,战争把它分成了两部分。居住在两边的人属于同一血统、同一文明,具有同样水平的技术和知识。哪一部分兴旺了,哪一部分不得不用墙来把它的公民关在里面,哪一部分今天必须用武装警卫并借助猛犬和地雷来对付那些勇敢而绝望的公民,他们宁愿冒生命的危险要离开他们的共产主义天堂,投向墙那边的资本主义地狱。
【按:这里都被删除了,哎!】
在墙的一边,街道灯火辉煌,商店里满是熙熙攘攘、兴高采烈的人群。一些人在购买来自全球的货物。另外一些人奔向众多的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他们可以自由地买到表达各种意见的报章杂志。他们可以互相或同陌生人交谈任何问题,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各种见解。走上几百步,排上一小时的队,填好表格,领到要交回的通行证,你就可以象我们那样去到墙的另一边。那里,街道是空荡荡的;城市灰色而苍白;商店的橱窗毫无生气;建筑物表面积满了污垢。三十多年了,战争的破坏还没有修复。在东柏林短暂的访问期间,我们发现,洋溢着欢乐气氛的唯一地方是娱乐中心。在东柏林呆上一小时就足以理解为什么当局要修建那堵墙了。
西德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从一个被打败和被摧残的国家变成欧洲大陆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是自由市场创造的奇迹。当时德国的经济部长是个经济学家,名叫路德维希·艾哈德。1948年6月20日是星期天。在这一天,他下令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就是今天的西德马克,同时取消了差不多所有对工资和物价的管制。正如他常说的那样,他之所以在星期天采取行动,是因为法、美、英占领军当局星期天不办公。他深信,要是在其他日子采取行动,那些对管制抱赞同态度的占领军当局准会取消他的命令。他的措施象是具有魔力。几天之内,商店里便摆满了货物。几个月之内,德国的经济就活跃起来了。
即便是两个共产党国家苏联和南斯拉夫,也形成了类似的对比,虽然不那么极端。苏联是严格地由中央控制的。它没有完全取消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但它尽可能地限制它们的范围。开始时,南斯拉夫走同样的道路,但在铁托同斯大林的俄国破裂之后,它急剧地改变了它的路线。它仍是共产主义的,但谨慎地实行分散化并运用市场力量。大部分农田归私人所有,其产品可以在比较自由的市场上出售。私人可以经营雇工不超过五人的小企业。小企业,特别是手工业和旅游业方面的小企业获得了很大发展。大企业是工人合作社——一种效率不高的组织形式,但至少使个人能在一定程度上肩负责任并发挥主动精神。南斯拉夫的居民是不自由的。他们的生活水平比邻国奥地利或其他西方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低得多。然而,南斯拉夫还是给从俄国去的有观察力的旅游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较之下它是天堂。
在中东,尽管以色列宣布的是社会主义的哲学和政策,并且政府广泛地干预经济,但它仍然具有强有力的市场因素,这主要是对外贸易在以色列的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产生的间接后果。它的社会主义政策妨碍了它的经济成长,但是它的公民比起埃及的来,享有更多的政治自由和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埃及的政治权力更比以色列集中得多,其经济活动受到的控制也要比以色列严格得多。
在远东,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和日本,都广泛地依赖私人市场,因而都很兴旺发达。它们的人民充满希望,经济正在迅猛发展。最好的衡量标准是,七十年代后期,这些国家平均每人的年收入,最低的约达七百美元(马来西亚),最高的约达五千美元(日本)。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共产党中国都严重依靠中央计划,因而都经历了经济停滞和政治压制。这些国家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不到二百五十美元。
主张中央经济计划的知识界人士曾经为毛的中国高唱赞歌,可没想到毛的继承人则大讲中国的落后并埋怨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没有取得进步。他们所设想的促进现代化的措施之一,就是让物价和市场起比较大的作用。同在南斯拉夫一样,这种策略将使中国当前低下的经济水平大大提高。但是,只要对经济活动仍保持严格的政治控制,私有财产仍受严密限制,这种提高就将大大受到限制。而且,即使是在这样有限程度上放出个人积极性的妖怪来,也会引起政治问题,迟早大概会产生反应,导致更大的独裁。另一种结果,共产主义垮台,被市场制度所取代,看来远不那么可能,虽然作为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并不完全加以排除。同样,一旦年迈的铁托元帅去世,南斯拉夫将经历政治上的不稳定,可能产生反应,导致更大的独裁,或者远不那么可能的,导致现存集体主义的安排的破产。
【按:这里都被删除了,哎!】
值得更详细地考察的一个特别显明的例子,是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对比——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最初三十年的经历,和日本在1867年明治维新后最初三十年的经历。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般说来很难象物理学家那样作有控制的实验,这种实验在验证假设上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在这里,经验产生的一些东西,很接近于有控制的实验,我们能够用以检验经济组织方法上的差别的重要性。
中间相隔八十年。但在所有其他方面,在我们拿来比较的开始时期,两国的情形很相象。两者都有古老的文明和发达的文化。两者都有高度结构化的人口。日本是封建结构,有大名(即领主)和农奴。印度是严格的等级制,按照英国人“排定的等级”,最上面是婆罗门,最底下是贱民。
两个国家都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革,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安排方面发生剧烈的变动。在两国内,都有能干的、虔诚的领袖掌权。他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决心使经济的停滞变成迅速的增长,把他们的国家转变成大国。
几乎所有的差别都对印度,而不是对日本有利。日本先前的统治几乎使它同其余世界完全隔绝,国际贸易和接触限于一年一次的荷兰船只的访问。少数被准许呆在那个国家的西方人,被圈在大阪港口一个小岛上的居留地内。三个多世纪的强行隔绝,使日本对外部世界茫无所知,在科学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除中文外,几乎没有人能够讲或者读外语。
印度要幸运得多。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得到巨大增长。这种增长,在两次大战之间因从英国争取独立的斗争变成停滞,但并没有倒退。运输的改进结束了过去反复发生的地区性饥荒。它的许多领袖曾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受教育,尤其是在英国。英国的统治留下了一批高度熟练和有训练的民政人员、现代的工厂和一个非常完好的铁路系统。这些在1867年的日本一样也没有。印度在技术上虽比西方落后,但差距小于1867年的日本同当时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
印度的物质资源也比日本优越得多。日本在物质资源上的唯一优势大概是海洋,使得交通方便并提供大量的鱼。日本只有此一项优势,其他全不如印度。印度的幅员约为日本的九倍,而且有大得多的面积是比较平坦和交通便利的土地。日本则大部分是山区,它只沿着海岸有一条狭长的可居住和可耕种的地带。
最后,日本没有得到半点外援。在日本没有外国投资,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或基金会赠款给日本或提供低利贷款。它不得不依靠自己筹措资金来发展经济。它也曾有过一次幸运的例外。在明治维新后的早期,欧洲的蚕茧严重歉收,这使得日本能够靠出口生丝赚得比平时要多的外汇。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偶然的或有组织的重要的资金来源。
印度的境况要好得多。自从1947年独立以后它从世界上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大部分是赠送的。这种输送现在也还在继续着。
尽管1867年的日本和1947年的印度情况相似,其结果却大不相同。日本摆脱了封建结构,让所有的公民都有社会和经济的机会。普通老百姓的境况迅速改善,虽然人口陡然增长。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本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虽然它没有实现完全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但在这方面却取得了巨大进展。
印度口头上废除等级限制,但实际上很少进展。少数人和多数人在收入和福利方面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象八十年前的日本一样,印度的人口猛增,但按人口平均的产量却没有按同样的速度增长。其经济仍然近乎停滞。那最贫穷的三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英国统治结束后,印度曾夸耀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没过多久,就开始实行独裁统治,限制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目前,它正处于重新这样做的危险之中。
怎样解释这两种结果的差别,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人的性格所造成的。据说,宗教戒律、等级制度、宿命哲学——所有这些把印度人民禁锢在传统的束缚之下。据说印度人缺少进取心而且懒惰。而日本人则受到称赞,说他们有干劲、精力旺盛、热心于接受外来的影响,而且难以置信地善于把从外边学到的东西加以改造利用。
关于日本人的这种描绘在今日可能是对的。但在1867年却不是这样。当时居住在日本的一个外国人写道:“我们不认为它(日本)会变得富有。自然赋予的长处,除了气候,以及人民自己的爱好懒惰嬉戏,妨碍了它。日本人是一个愉快的种族,有一点就满足,不大可能取得很大成就。”另一个写道:“在世界的这部分,西方确立和公认的原则,好象失去了它们原先具有的效力和活力,并致命地倾向于芜杂和腐败。”
同样,关于印度人的描绘也可能符合今天印度国内的一些印度人,甚至可能符合大多数,但它肯定不符合侨居别处的印度人。在许多非洲国家,在马来西亚、香港、斐济群岛,巴拿马以及新近在英国,印度人是成功的企业家,有时候还成了企业界的台柱子。他们常常是发动和推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印度国内,只要是能避开政府控制的铁手的地方,事业心、积极性和干劲都有所表现。
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不取决于群众的品行。在每一个国家,一小部分人确定步子,决定事件的进程。在发展得最快最成功的国家里,一小部分事业心强、甘冒风险的人闯在前面。为仿效者创造跟随的机会,使大多数人得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率。
许多外界观察者探讨的这种印度人的特征,与其说是缺少进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其反映。当卖力干和冒风险得不到报酬的时候,懒惰和消沉就会滋生。宿命的哲学是同停滞相适应的。印度并不缺乏人材,能发动和推进经济发展,就象日本在1867年所经历,或者甚至象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经历的那样。的确,印度的真正悲剧是,它本可以——我们相信——成为一个繁荣昌盛而生气勃勃的自由社会,但目前却仍然是一个满是穷困潦倒的人民的次大陆。
我们新近碰到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经济制度如何能够影响人的性格。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流入香港的中国难民,推动了它的经济飞快发展,并以他们的积极性、事业心、勤俭和干劲得到了应有的尊敬。中国新近放宽对移民的限制之后,产生了一批新的侨民——来自同一种族,具有同一基本的文化传统,但经过三十年共产党统治的抚育和塑造。我们听到一些雇用这些难民的公司说,他们与早先来香港的中国人大不相同。新来的移民非常缺少主动性,需要人家确切告诉他做什么。他们懒惰,不合作。无疑,在香港的自由市场呆上几年之后,他们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的。
那么,对于1867年至1897年的日本和1947年到现在的印度之间的不同经验该作何解释呢?我们相信,其解释同东西德之间、以色列和埃及之间以及台湾和红色中国之间的差别一样。日本按照当时英国的模式,主要依靠自愿的合作和自由市场。印度则按照当时英国的模式,依靠中央经济计划。
明治政府也曾多方面进行过干预,在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它送许多日本人出国接受技术训练,邀请了许多外国专家。它在许多工业中建立了领头的工厂,并给与其他工业许多补助。但是没有哪个时候它曾经试图控制投资的总额或方向或是生产的结构。国家只在造船业和钢铁业保持大量的股权,因为它认为这是军事力量所必需的。它维持这些工业,因为它们对私人企业没有吸引力,需要大量的政府补助。这些补助消耗日本的资源。它们妨碍而不是刺激日本经济的进展。最后,一项国际条约禁止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头三十年征收高于5%的关税。这种限制证明对日本完全是一件好事,虽然当时曾遭到埋怨,而且在条约的限制期满后就提高了关税。
印度执行了一条与此大不相同的政策。它的领袖们把资本主义看作帝国主义的同义语,不惜任何代价要加以避免。他们制订了一系列俄国式的五年计划,详细地规定了投资项目。某些领域的生产为政府所保留;私人公司容许在其他领域经营,但必须同计划一致。关税和限额控制了进口,补贴控制了出口。自给自足是理想,不用说,这些措施造成外汇短缺。这又用严密而广泛的外汇管制来对付,外汇管制成了无效率和特权的一大根源。工资和物价受到管制。要盖个工厂和进行其他投资必须得到政府批准。无处不有的税,纸面上定得很高,实际上大量逃漏。各种各样的走私、黑市和非法交易,就象赋税一样无处不有,破坏了法制的威信,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中央计划的死板,使得有可能满足紧急的需要,从而起了有价值的社会作用。
在日本,依靠市场,挖掘了潜在的、意想不到的能力和才干的资源。它阻止了妨碍改革的既得利益。它强使发展接受效率的严峻考验。在印度,依靠政府的控制,挫伤了积极性或将它付诸东流。它保护了既得利益不予改革。它用官僚主义的批准代替市场的效能,作为生存的尺度。
这两个国家的家庭纺织品和工厂纺织品的经历可以说明政策上的区别。1867年的日本和1947年的印度,家庭纺织业的规模都很大。在日本,外国的竞争没有对家庭生产的生丝产生多大影响,这也许是因为日本的生丝优越,加上欧洲的歉收;但它几乎完全排挤了土制棉纱,后来又排挤了土布。日本的纺织业工厂发展起来了。开始它只制造最粗糙的、最低档的纺织品。后来制造越来越高级的纺织品,最后成了一门大出口工业。
在印度,手工纺织得到补助并保证有其市场,据说是为了缓和向工厂生产的过渡。工厂生产逐渐增加,但为了保护手工纺织业,被有意地加以限制。保护意味着扩大。手工织机从1948到1978年大约增加了一倍。今天,在全印度成千上万的村庄里,从早到晚可以听到手工织机的声音。如果是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其他工业竞争,有一门手工纺织业并不坏。在日本,现在还存在一门虽然极小但是兴旺的手工纺织业。它织造高级的丝绸和其他织品。在印度,手工纺织业的发达是因为得到政府的补助。实际上,政府向那些生活并不比手工织机工人好的人征了税,以使手工织机工人的收入高于他们从自由市场上赚得的收入。
十九世纪初期英国面临的问题,同几十年后日本所面临的和一个多世纪后印度所面临的问题正好一样。动力织机有摧毁兴旺的手工纺织业的危险。英国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这门工业。它显然考虑了印度采取的那种政策:补助手工纺织业,保证它的市场。但该委员会立即否定了这项政策,理由是这只会使根本的问题——手工织工过多,变得更严重。这正是印度所发生的情况。英国采取了同日本一样的解决办法——暂时是严酷的,但最后是慈善的政策,让市场力量起作用。
印度和日本的这种对比很有趣,因为它不仅如此清楚地表明两种组织方法的不同结果,而且表明在追求的目标和采取的政策之间并无关系。明治维新统治者——他们立志要加强他们国家的权力和荣誉而很不重视个人自由——的目标同印度的政策更合拍,而不是同他们自己采取的政策。印度的新领袖们——他们热衷于个人自由——的目标同日本人的政策更合拍,而不是同他们自己采取的政策。
控制和自由
美国虽然没有实施中央经济计划,但在过去五十年里,我们在经济中扩大政府的作用已经够多了。这种干预使我们在经济上付出了很大代价。对经济自由施加的限制,使我国两个世纪来的经济发展有归于结束的危险。干预也使我们在政治上付出了很大代价。它大大地限制了我们的个人自由。
美国主要还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世界上最自由的大国之一。但是,正如林肯在那有名的“分裂的家”的演说中所说:“一个家分裂开来反对自己,就不能维持。……我不期望这个家会垮掉,我确实期望它不再分裂。它要么完全归一,要么完全变样。”他是在讲对人的奴役。他的预言同样适用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要是在这方面走得太远,我们分裂的家会倒向集体主义一边。幸运的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公众正在认识到这个危险,决心阻止并扭转政府干预越来越多的趋势。
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现状的影响。我们倾向于这种看法:当前的局面是理所当然的,是事情的正常状态,特别是当事情是由一系列小的和渐进的改变来形成的时候更是如此。要估计那累积起来的影响有多大是困难的。需要发挥想象力,超脱现状,用新的眼光来加以观察。这是很值得做的事情。结果要不是令人吃惊的话,大概也是会出人意外的。
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自由选择如何使用我们的收入:多少用在我们自 己身上,花在什么项目上;多少存起来,用什么方式;多少给别人,给谁。现在,我们收入的40%以上是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代表我们花掉的。有人曾提出规定一个新的国庆日,叫个人独立日——在每年的这一天,我们不再为政府的开支而工作……而是为了支付几个人或单独一个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愿望选定的项目而工作。”在1929年,这个节日也许应该定在2月12日,林肯的生日这一天;今天,也许应该定在5月30日;如果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到1988年左右它会碰上另一个独立日,7月4日。
自然,我们对政府代表我们花多少我们的收入,有一些发言权。我们参与了那个政治过程,这个过程使政府花费了我们 40% 以上的收入。多数通过的办法是一种必要和可取的权宜之计。但是这同你在超级市场上买东西时的那种自由很不一样。当你一年一度去投票的时候,几乎总是投一揽子的票而不是投特定项目的票。如果你是多数,最好的情况是,你在得到你所愿意要的项目的同时也将得到那些你反对的项目,只是比较起来不认为那么重要罢了。通常的结果是,你得到的东西并不是你当初投票赞成的东西。如果你是少数,你就必须服从多数的表决,等待下一次机会。当你每天在超级市场上投票时,你得到的就是你投票要的东西,别的人也是一样。投票箱产生的是遵守而并不一致,市场产生的是一致而无遵守。这就是为什么要尽可能把表决方法只用于那些必须遵守的决定的原因。
【按:新版翻译是“投票箱产生的结果是被迫一致而非自愿一致,而市场产生的结果则是自愿一致而非被迫一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仅在需要被迫一致才能做出决策的时候才选择投票箱这种办法,而且能不用就不用。”】
作为消费者,我们甚至不能自由选择怎样使用纳税后剩下的那部分收入。我们现在不能自由购买甜味素,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连糖精也不能随意购买了。我们的医生不能自由地为我们开许多药,尽管他认为这些药对我们最有效,或者这些药在国外已经广为使用了。我们不能自由地购买一辆没有座位安全带的汽车,虽然眼前我们仍可以自由选择是系它还是不系它。
经济自由的另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按照我们自己对价值的看法自由地使用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自由从事任何职业,加入任何企业,同任何别人作买卖,只要是在严格自愿的基础上这样做,不诉诸强力来强制别人。
今天,你不能自由地作为一个律师、内科医生、牙科医生、管子工、理发师、殡仪人提供你的服务,或是从事其他许多职业,除非先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批准或证书。你不能自由地按照你同你的雇主协商好的条件加班,除非条件符合政府官员定下的规章。
你不能自由地设立银行、进入出租汽车行业或从事出售电力或电话服务的企业或经营铁路、公路或航线,除非先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
你不能自由地在资本市场筹集资金,除非你填好证券交易委员会需要的多种表格,而且能使证券交易委员会满意于你提出的计划书。该计划书必须把前景描绘得如此暗淡,以至没有哪一个头脑清醒的投资者会愿意对你的计划投资,才会使证券交易委员会满意。而且,要取得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批准,可能得花费十万多美元——这肯定会吓退我们的政府声称要资助的小企业。
拥有财产的自由是经济自由又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们的确广泛地拥有财产。我们当中的多数人拥有所住的房子。但是谈到机器、工厂和类似的生产手段,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们自称是一个私人企业的自由社会,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但就公司企业的所有权来说,我们大概46%是社会主义的。拥有1%的股份意味着你有权分到1%的利润,并必须用你全部资产的价值分担1%的损失。1979年联邦的公司所得税率是十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必须缴纳46%的所得税(1979年以前为48%)。联邦政府从每一美元的利润可得四十六美分,它也分担每一美元损失的四十六美分(如果有早先的利润可以抵消这种损失的话)。联邦政府拥有每一公司的46%——虽然不是以直接参预决定公司事务的形式。
甚至仅是列举出加于我们经济自由的全部限制,也得一本比此书更厚的书,更不用说来详细描述了。上述例子只是用来说明,这种限制已变得多么普遍。
人类自由
对经济自由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影响一般的自由,以至言论出版自由也受到了影响。
让我们看一看下面这些从李·格雷斯1977年的一封信中摘出来的话,他是那时一个石油 煤气协会的执行副会长。关于能源立法问题,他写道:
如你们所知道的,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一千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应该定多高价格的问题,而是宪法第一号修正案的延续,即保障言论自由的问题。随着限制的增加,就像老大哥越来越紧地盯着我们,我们胆怯起来了,不敢说出真相,不敢揭露谎言和错误。我们对国内收入署的查帐、官僚主义的扼杀或政府的刁难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心理是反对言论自由的一项强大的武器。
10月31日(1977)出版的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华盛顿小广播”栏里指出:“石油业的职员们声称,我们接到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的最后通碟:‘支持政府提出的原油税——不然就要面临更严格的规定和可能发动的一场运动来拆散石油公司’。”
他的判断为石油业人员的公开行为所充分证实。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斥责他们赚取“污秽的利润”,一批石油业的经理中间竟没有一个人顶他,或是退出会议室,拒绝再受人身攻击。石油公司的经理们私下对现行限制他们活动的复杂的联邦控制结构或卡特总统提出的大大扩大政府干预的办法,表示强烈的反对,但却发表措辞温和的公开声明,赞成控制的目标。
几乎没有企业家认为卡特总统的所谓自愿的工资物价管制是对付通货膨胀的可取的或有效的办法。然而,他们却争先恐后地颂扬那个计划,并答应予以合作。只有少数人,如前国会议员、白宫官员和内阁成员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有勇气公开加以谴责。另一个敢于讲的人是那个八十高龄的执拗的前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
为了言论自由,人们完全应当付出代价——如果只是不吃香、挨批评的话,也许还能忍受。但这代价应当是合理的而不是过分的。决不应该如有名的最高法院裁决所说的对自由言论产生“令人胆寒的影响”。然而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是,当前对企业的经理们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影响。
这“令人胆寒的影响”并不只限于在企业经理们身上。它影响我们全体。我们最熟悉学术界。我们的同行中间,有许多人,搞经济学的和自然科学的得到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补助;搞人文的得到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补助;所有在大学教书的教师都从州的立法机关那里得到他们的一部分薪金。我们认为,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对高等教育的税款补助都是不可取的,应当予以取消。这无疑在学术界还是一个少数人的意见,但这个少数人比人们从公开声明中所能搜集到的要多得多。
新闻界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政府——不仅作为主要的新闻来源是这样,而且在许多日常事务中也是这样。看一看英国的一个惊人的例子。伦敦《泰晤士报》这样一份大报,几年前有一天被它的一个工会阻止不能出版,原因是该报打算发表一篇报道,讲工会企图影响报纸的内容。结果,劳资纠纷使这家报馆完全关闭,有关的工会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得到政府的特别的庇护。英国一个全国性的记者联合会正在发起成立记者组织,并威胁要抵制那些雇用不属于他们这个联合会的人员的报纸。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个堪称为自由发祥地的国家里。
就宗教自由来说,在美国,阿密希的农民的房屋财产曾被没收,因为他们以宗教的理由拒绝交纳社会保险税——也不接受社会保险。教会学校的学生曾被作为逃学者、违反强制上学法被传讯,因为他们的教师没有那必要的纸片,证明他们满足了州政府的要求。
【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只是一句口号。。】
虽然这些例子只是反映了些表面的现象,它们却说明了基本的道理:自由是个整体,任何事情如果减少我们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自由,它也就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自由。
自由不可能是绝对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社会中,对我们的自由施加某些限制是必要的,以免遭受其他更坏的限制。但是,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一点,当今迫切需要的是取消限制而不是增加限制。
本节内容概述
自由贸易不仅能促进我们的物质福利,而且还能促进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协调,鼓励国内的竞争。
主张征收关税的,只有三个论点在原则上还多少站得住脚。
第一个就是国家安全论。
第二个是“幼稚产业”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提出过这个论点。
第三个不能立即排除的主张征收关税的论点是“以邻为壑”论。
互加关税----这种报复行动不但不会使其他国家减少限制,相反,只会招致更多的限 制。
我们可以告诉全世界:我们信仰自由并愿意实行。我们不能强迫你们实行自由。但我们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一切人提供充分的合作。我们的市场对你开放,没有关税或其他限制。你能够并愿意卖什么,就来这里卖好了,你能够并愿意买什么,就来这里买什么好了。这样,个人之间的合作就会成为世界范围的和自由的合作。
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上,就如在任何国家的自由经济中一样,交易在私有的实体——个人、企业、慈善机构——之间进行。任何交易的条件,都由参加各方协议。除非各方都相信他们能从交易中得到好处,否则就做不成交易。结果,各个方面的利益取得了协调。普遍存在的是合作而不是冲突。
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公民同集体主义国家的公民之间,不可能进行完全的私人交易。有一方必定得由政府官员为代表。政治考虑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实行市场经济的政府容许其公民尽可能直接地同集体主义的政府作交易,摩擦可以减少。要想用贸易作为政治武器或用政治措施作为手段来增加同集体主义国家的贸易,那只会使不可避免的政治摩擦变得更厉害。
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不取决于群众的品行。在每一个国家,一小部分人确定步子,决定事件的进程。在发展得最快最成功的国家里,一小部分事业心强、甘冒风险的人闯在前面。为仿效者创造跟随的机会,使大多数人得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率。
不施加关税对相关产业的冲击----暂时是严酷的,但最后是慈善的政策,让市场力量起作用。
经济自由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自由选择如何使用我们的收入;经济自由的另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按照我们自己对价值的看法自由地使用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自由从事任何职业,加入任何企业,同任何别人作买卖,只要是在严格自愿的基础上这样做,不诉诸强力来强制别人。
自由不可能是绝对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社会中,对我们的自由施加某些限制 是必要的,以免遭受其他更坏的限制。但是,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一点,当今迫切需要的 是取消限制而不是增加限制。
附录英国“自由贸易”的真相
只能说当时英国的经济自由度显然高于其他国家,但英国本身离自由贸易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可以说当时各国的关税税率显著低于当前关税税率,不能说当时美国之类的实行的也是自由贸易。
如下片段来自英国历史学者约翰·霍布森的代表作《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11出版)一书: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1846 年并不标志着英国向自由贸易的转变。1846 年至 1860 年之间,英国关税保持在 20% 的高额水平,1860 至 1879年间仍保持在高达 10% 的水平。只在 1880 至 1913 年期间才降到适度的 6%。 …… 总之,关于英国工业化是基于放任主义的传统描述,虽然广为人知,但只是一种神话。英国的税收、关税、预算、赤字、国债和军事支出等因其数额之高而引人注目。
附录自由贸易的起源——儒学
详见第一章附录。
儒学强调「通商惠工」、「关市讥而不征」、「民富国富」,显然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
【李竞恒】《“关市讥而不征”: 原始儒家为何反对征收关卡税》
在张家山汉简《算数书》中,记载了战国末或汉初的关卡收税算术题,说商人带着盾、狐、狸、犬出关,要缴纳租税“百一十一钱”,百姓如果背着米出关,要经过三个关卡,“三税之一”,即三分之一的份额都要被榨取。
孟子认为,只要能更好地保护民间商业,废除沉重的关卡税,就会“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者皆欲出于王之涂”。
孟子主张自由贸易。在《孟子·梁惠王下》提出治国需要“关市讥而不征”,在《尽心下》中,他提出“古者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意思是古代建立关隘,是为了保护社会,而不是为了多收税,他主张对民间商业不收关隘税。这一点与英国《大宪章》第13条,免除各市、区、镇、港的关卡税,皆享有免费通关权的主张是一致的。
在商贸道路上设立关卡,孟子认为其功能是稽查犯罪即可,而不是用来收税,增加贸易负担。从考古资料来看,当时关卡商业税的负担不小。如包山楚简《集箸》简149记载了十个邑、四条水道日常都要收取“关金”,可见当时官府不但在陆地上收取关卡税,在水路上一样要榨取一笔。
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楚王颁发给鄂君启的车节和舟节,都有错金铭文,车节铭文云“得金节即毋征”,“不得其节即征”,意思是鄂君启这种特权者拿着楚王颁发的“金节”这一凭证,在通过关卡时就能享有不征税的特权,舟节铭文云:“见其金节毋征,毋舍桴饲;不见其金节则征。如载马、牛,差以出内关,则征于大府,毋征于关。”意思也是水路关卡上,凭借特权金节可以免除征税,但如果运载牛、马出关则由大府征税。显然,鄂君启这种特权者是极少数,绝大部分的普通商旅、百姓无论是走陆路还是走水路,经过各国关卡都是要遭受盘剥的。所谓“平民百姓不似鄂君启之权贵,通商行旅是要遭到重重关卡征敛的”。
在张家山汉简《算数书》中,记载了战国末或汉初的关卡收税算术题,说商人带着盾、狐、狸、犬出关,要缴纳租税“百一十一钱”,百姓如果背着米出关,要经过三个关卡,“三税之一”,即三分之一的份额都要被榨取,可见是民众和商旅的沉重负担。而特权者却并不缴纳通关税,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对于沉重的关卡之税,战国时期的思想中有批评的声音。如上博楚简《容成氏》是一篇带有儒家思想倾向的出土文献,其中就专门讲到了美好的大禹时代“关市无税”,不征收关卡税,而到了夏朝末年的桀王则相反,“以征关市,民乃宜怨”(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
孟子生活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自然会对沉重的关卡税提出批评。孟子的主张就是,各个关卡,无论贵族还是普通商人,都统统不收税,藏富于民,保护自由贸易。所以梁启超先生对这一主张的评价是:“儒家言生计,不采干涉主义”(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0页),可谓一语中的。孟子认为,只要能更好地保护民间商业,废除沉重的关卡税,就会“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者皆欲出于王之涂”(《孟子·梁惠王上》),天下的百姓、商人都希望来这个低税率和保护自由贸易的国家,行走在畅通无阻的陆路和水道上,市场则会进一步繁荣,国家经济发展了,其实长远对国家才有好处。
《孟子·公孙丑上》记载了孟子的商业思想:“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对于“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有不同说法。
笔者认为,对这一段解释比较合理的就是朱熹引用张载的注释“赋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货;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赋其廛”,“廛”是市场中的商业用地(邬勖:《秦汉商业用地制度初探:以出土文献为中心》),意思就是对市场商业用地只征收一点商业用地税就行了,不用征收货物税,此外要用市场法律提供守夜人最低秩序,而不再征收其它多的税赋。这种低税收和良好公共服务的状态,能吸引到各国的人都前来参与市场活动,促进经济的繁荣。
奥地利学派谈到,远古以来的人无法理解商业活动的实质。他们看到商业“贱买贵卖”,因此将其视为一种可怕的魔法。西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对商人表示藐视。西方的两希传统中都镌刻着蔑视商业活动的基因: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嘲讽商人是“是些身体最弱不能干其他工作的人干的”,耶稣则把商贩驱逐出圣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孔子、孟子那里从来没有对商人或商业行为的讥讽,相反,孔子经常熟练使用商业术语,原始儒学的贤人中更是出了儒商子贡,而到了孟子这里仍然强烈地为自由贸易进行辩护,这种对市场的态度,是原始儒学的重要属性之一。
附录联邦德国战后崛起之路
路德维希·威廉·艾哈德(德语:Ludwig Wilhelm Erhard,1897年2月4日—1977年5月5日),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被誉为“社会市场经济之父”。他从1949年到1963年被任命为联邦德国(西德)经济劳动部长,从1963年到1966年担任联邦德国(西德)总理。
从1945年到1946年,艾哈德在巴伐利亚州任商业和企业部部长,但这段时间里他的工作的成绩不大。
1947年,他领导英美占领区管理部门的特殊货币和贷款专家委员会研究货币改革。
1948年3月2日,德国自由民主党提名艾哈德为美英法联合占领区所组成的联合经济区的经济管理部门首长,这样艾哈德实际上就成为西部占领区的经济政策负责人。在西德进行货币改革前五天(1948年6月20日),占领国代表才通知他这项措施的实行。6月19日,艾哈德通过电台宣布取消价格约束和义务提供服务的规定。第二天美国占领军司令愤怒地将艾哈德招来训斥他自主改变了占领军的命令。艾哈德回答说:“我没有改变这些命令,我废除了这些命令。”今天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艾哈德的这个自主行动是后来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主要条件。
艾哈德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奠基人之一,他召集了威廉·勒普克等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为经济部副部长,他们对德国开始时期的经济政策的影响非常大。艾哈德本人始终反对将当时德国经济的发展称为“经济奇迹”,他本人总是说,世界上没有奇迹。他认为这个发展是成功的市场经济政策的结果。
附录柏林墙
柏林围墙又称柏林墙(德语:Berliner Mauer)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期间,隶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政府环绕西柏林边境修筑的全封闭边防系统。它最早建于1961年8月13日,全长167.8公里,最初以铁丝网和砖石为材料,后期加固为由瞭望塔、混凝土墙、开放地带以及反车辆壕沟组成的边防设施。东德政府称此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德语:Antifaschistischer Schutzwall)和“强化边境”(德语:Befestigte Staatsgrenze),建造柏林墙的目的在于阻止东德居民通过西柏林前往西德。因为柏林墙把西柏林地区如孤岛一般地包围封锁在东德范围之内,所以也被称之为“自由世界的橱窗”(德语:Schaufenster der freien Welt)。它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更是分割东西欧的铁幕的象征。
柏林墙的建立是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之间冲突导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纳粹德国首都柏林被分割为东柏林与西柏林;在柏林墙修建之前,共计约有350万东德居民逃离苏占领区以及之后的东德,其中1949年到1961年逃离的人数约为260万。此外还有大量波兰人与捷克斯洛伐克人将柏林视为其通往西方的通道。许多人通过西柏林前往西德和其他西欧国家。柏林墙修建后在1961至1989年间这类逃亡被大幅限制下来,约有5,000人在此期间尝试翻越柏林墙。1962年起《开枪射击令》生效,东德边防军允许对非法越境者开枪射击,此举于1982年甚至通过立法被合法化。据截止2009年的统计,被枪杀人数约在136人至245人之间,确切死亡人数目则不得而知。
1989年东欧国家发生了一系列政治变革,邻国波兰和匈牙利政府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在数周的抗议活动后,1989年11月9日东德政府宣布允许公民申请访问西德和西柏林,当晚柏林墙在东德居民的压力下被迫开放。随后数周中欣喜的人群凿下柏林墙作为纪念品,1990年6月东德政府正式决定拆除柏林墙。柏林墙的倒塌为结束东德共产党的统治、东德政府的倒台以及两德统一奠定了基础;1990年10月3日,两德正式统一,而柏林亦成为两德统一后的新首都。
柏林墙建立后,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其中死亡人数存在一定争议。查理检查站博物馆负责人希尔德布兰特称死亡人数多于200人,波茨坦的当代历史研究中心(ZZF)已确认136人死亡,先前的官方统计为96人。
东德政府向边防守卫下达了《开枪射击令》,虽然随后东德官员否认这一命令的存在。研究者发现在一封1973年10月的命令中,守卫被告知尝试穿越围墙的人为罪犯,并且需要开枪射击:“使用你的武器时不要犹豫,即使违反边境禁令的是一队妇女和儿童,这是叛徒们常用的策略。”
早期围墙尚未修建时,东德的人们通常通过跳过铁丝网和从公寓窗口跳下来穿过边境,然而在柏林围墙修建后这种方式几乎绝迹。东德当局不允许靠近边界的公寓继续正常使用,并且用砖封住了边境附近建筑物的所有窗口。在得知柏林围墙修建消息的第三天,19岁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防军士兵康拉德·舒曼便跳跃过了当时低矮的铁丝网边境,进入西柏林。这一瞬间被西方媒体记者抓拍到,此事也成为了冷战期间西方用来广为宣传的样本。他也是第一个越境的边境守卫。艾达·西格曼为第一个因穿越围墙而丧生的人,她在1961年8月22日从柏尔诺街48号的三层公寓跳下后身亡。1961年8月当柏林墙建立起来之后,东德边防军就得到了开枪射杀所有尝试越境者的命令。1962年8月17日彼得·费希特尔试图翻越围墙逃往西柏林,在攀至顶部后被东德边防警察发现并开枪射杀。当时,东西两边的人民都看到他中枪,并有西方记者在场。西柏林边防军曾投掷急救包,并甚至有警察翻身跃墙将这位东德青年抬起来企图抢救,但东面却没有人施予援手,事件在冷战时期轰动一时,他成为了第一个因试图攀越柏林墙而被射杀的人。最后一个被射杀的人是1989年2月6日尝试越境的克里斯·格弗罗伊。
1997年3月,两名开枪的东德边防军士兵罗夫·费特列治和埃里克·薛伯分别被判刑20和21个月。
除直接翻越外,人们采取了许多方式尝试越境。1963年4月19岁的国家人民军的文职人员沃尔夫冈·恩格斯曾利用所在基地的苏联装甲运兵车冲破围墙,随后被东德边防军开火并击伤,最终被西德警察解救。托马斯·克鲁格曾利用东德体育技术协会的兹林Z 142轻型飞机穿越柏林墙降落在英国皇家空军位于加托的基地。另外有人通过挖地道、大型热气球、潜水以及利用汽车高速冲过检查站的方式越境。随后东德在检查站修筑了之字形的道路并降低了横杆的高度。由于下水道系统尚为柏林墙修建前的结构,部分人通过Girrmann学生组织的协助利用下水道越境。
附录大逃港
逃港,即逃亡至英属香港,中国大陆称“大逃港”,在香港又称为偷渡潮,是指在1950年代至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大量中国大陆民众尝试偷渡至英属香港之现象。自1951年中英封锁边界开始,共出现四次大规模的偷渡,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实行人民公社化期间;第二次是1961年开始,至三年大饥荒后1962年;第三次是1972年;第四次是1979年,大量人口逃港的原因,是为了摆脱贫穷和饥饿。逃港潮也促使并强化了英属香港的反共意识形态。
逃港者以最临近香港的广东人为压倒性多数,其次来自福建和四川(包括今重庆),后者比较多用合法途径。而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前后之移民以江浙(包括上海人)、山东、河南和天津为主。
由广东省偷渡来港者超过二百万,不少经香港移居东南亚或偷渡到欧美国家,按地区而言,最多是惠阳地区(包括今惠州市、深圳市、东莞市、河源市等)、潮汕、佛山地区,江门五邑地区以及广州,其次亦有数十万北方人以及华中人经上海偷渡到香港,少部分直接偷渡到香港,例如倪匡由内蒙古经上海偷渡到香港,李摩西以及李鹏飞亦从上海偷渡到香港,其余南方各省亦有零散数万人经广州偷渡到香港[3],总和亦有数十万,而南方人大多经广州、中山偷渡香港,北方人大多经上海及杭州偷渡到香港,所以现今香港人包括各省籍人。逃港而又成功者以男性较多,但亦有女性[注 1]。逃港者多为农民,亦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4]
逃港分为多个阶段,其中有因为中国大陆政府为了清除国内反动势力而任由逃离,但更多是因为忍受不了饥荒、阶级斗争等压迫。
逃港者以年轻人为主,大多因为香港和中国大陆有近百倍收入差距、认为香港遍地黄金(如电影《打蛇》的钻石山的谣传和《我的大嚿父母》之角色定位“抛妻别子偷渡去香港寻金觅财的康伯”)、向往香港生活等原因而逃港,逃港者亦有其他年龄层的人,因为被批斗、饥荒、希望赚取金钱以改善自己以及家人生活等原因到港,而年轻人则因为生活经验较浅,大多不是亲属被批斗而是希望赚取更多的金钱而到港。
大量人在偷渡过程中被鲨鱼咬死、游泳气力不足淹死、跳火车时摔死[5]、在偷渡过程中与解放军以及英国啹喀兵、华人兵纠缠中互有死伤、根据电影《打蛇》的资料搜集,不少人还遭被称为“打蛇人”的香港黑社会掳掠后强奸、斩杀[6],最后大约200万[7]至250万[8]成功越过边防线偷渡至香港市区,祇计1962年的大逃港,日均五千“大军南下”[9],短短一个月便南逃十五万人,著名事件包括华山救亲[10]。
1962年5月14日,由于逃港人数太多,香港政府决定放弃“安置难民”,开始“即捕即遣”涌入之难民[11]。约三万逃港者集结在香港上水华山,疲惫饥饿,在山中喘息,等候从市区闻讯赶来之亲人接下山。[12]
5月15日,金庸旗下《明报》发表了首篇社评:“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明报报馆一度成为救援物资中心。5月16日,胡仙旗下《星岛日报》刊登了《百名难民寄语香港亲友》一文。宗教团体、乡亲组织、新闻媒体发起了“援助有困难的人民”行动[13],前后共有十几万人次,送衣、送食、送水到华山。市民用各种方法保护华山上之亲友,包括接走、匿藏家中或市区。[14]
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下,警察将一批批越境者强行拖上卡车,送到石湖墟收容营地。当时香港政府决定,偷渡者在送入收容营后,免费给予两餐丰盛之自助餐,等第二日派车由罗湖桥送返大陆。当夜有市民守在营外,据报载:“滞留(在营外)的市民不下三四千众。”“他们当晚就在露天卧睡。”市内不少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都熄灯闭门,以示同情。
翌日,上万市民手持饼干、面包、粮袋,当卡车长龙驶出营门,公路两旁粮袋齐飞、泪雨倾盆。突然,成百人冲出马路,躺在地上,以身阻截车队,许多越境者纷纷跳车逃跑。
据事后估计,前后共有约过半华山越境者,在市民帮助及警察“抓捕不力”下,最后得以进入市区。[15]
在19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逐步取得中国大陆的控制权后最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相关的军政人员,以及资本家、地主、富农等为了逃避新政权,南下逃到英国殖民地香港。根据大陆官方档案显示仅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发的四次大规模逃港潮中,逃港者人数就达56万人。[16]。由于人数众多,香港政府在1950年5月起开始限制大陆人来港,并暂置国军家眷于调景岭[17];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因应抗美援朝,及为了清除国民党余党的需要,并没有封锁边境,任由他们离开中国大陆,直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才开始收紧边境。而同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大陆发动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大量仍留在大陆的资本家、地主、富农、以至于国民党中抗日人士被清算并受到批斗迫害,导致一些人在边境封锁后通过各种方式逃离大陆,揭开了逃港序幕。
1950年代初期,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不久,政局未稳、经济活动疲弱、民生凋敝;再加上政治运动四起,大跃进运动导致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田地颗粒无收,四五月份又青黄不接,大陆居民苦不堪言,迫切盼望逃出饥饿和高压的生活。[1]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大量知识分子、异见者因此被打成“右派”受到迫害,引发第一次大规模以知识分子为主的逃亡潮。1957年6月底至9月底,大陆公民第一次大规模通过宝安县(今深圳市)越境逃亡到香港,历时3个月遭到镇压而平息[1]。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引发了大饥荒,许多广东农民为了生存,纷纷外逃,广东地方政府起初对此默许,直至伊塔事件发生后政策才收紧。此后的逃港活动基本是非法经济移民以及家庭团聚。
1962年4月26日,在宝安县,大陆从惠阳、东莞、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来的公民结成长队伍,扶老携幼,牵儿带女,大量涌向香港,一日成功逃亡达到4,000人,参与逃亡人数8,000人,但是,51,395个来自12个省、62个县市的中国大陆公民被迫遣返。[1]1962年4月29日,宝安县公安局的14人假扮外流群众,混入逃亡人群,进行研究和考察,得知发起逃亡运动的主要是19岁到40岁的青壮年,尤其是大学生。[1]1962年5月6日,港英政府看到来势汹汹的人流,感到恐怖和震惊,于是将抓捕的逃亡者全部遣送回宝安。[1]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作出指示:“为了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中共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1]1962年5月22日,广东省的一万余官兵开始集中清理逃亡者,51395人被送返家中。[1]1962年6月19日,东莞县委发出指示,“对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干部、教师一律开除公职,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对参与外流的农村基层干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停止职务的处分。”[1]
1979年,深圳刚刚建市,香港即将在1980年实施即捕即解。因而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生了大规模越境逃亡香港的事件,人数共计十万余人,逃亡成功人数4万余人。[1]根据中国大陆官方资料,只计1979年广州的逃港失败而被捕入狱者已达5万,全省(尤以珠三角为主)达30万[18]。
更有资料显示,逃港者冒着极大生命安全风险,如水路(大鹏湾一带)常有鲨鱼出没、或会受到边防士兵开枪射杀。
而逃亡失败或者被遣返之中国内地居民,在被遣送回乡之后则会被视为“阶级敌人”,在批斗会上进行批判和殴打[1],并会被“劳改”(监禁和劳动刑罚)。
香港偷渡潮在世界史中,是冷战的一部分,国际上有称深圳河为“中国的柏林墙[21][22][23]”,是共产主义地区人民逃往资本主义地区“投奔自由”的世界史中之一部分[24]的评价。
因为珠三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成为其中一个主要移民地方,由珠三角偷渡到港的人口亦包括各省籍人口,包括当年占领广州的山东兵等。逃港亦大大加重了广东籍人口在香港人的比例,现今香港人口中的新移民有57%来自广东(包括先聚居在珠三角的各省籍人),这些人口又大多来自亲属移民,占总亲属移民的84%[26],香港的贫穷新移民人口几乎全为逃港者大陆亲属,其他省籍的移民以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为主。因为逃港者在中国大陆经历过批斗、饥荒的日子,他们比没有经历过中共统治、在香港出生的香港人更讨厌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大陆人,不少有恐共、反共、厌共甚至仇共的心态[27],对中共及香港本地亲共势力充满戒心和厌恶。故而不少香港人不接受香港主权移交,以及主张香港和中国大陆保持距离,并且很多都反对自由行和中港融合。不少中产在六四事件后到九七主权移交前亦大量移民外国,当时因为香港楼价高企,由香港移居外国的人口主要为投资移民,他们不少已经在1997年前售出楼宇,以投资移民外国[28]。
广东省因为与香港相距较近,许多试图逃港的居民都逃亡成功,造成了广东省人口锐减,工厂停办,城镇居民减少。[1]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广州市视察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1]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亦形容此事是“人民用脚投票”,将偷渡潮定性为经济原因而非政治原因。加上中国内地政府亦不想让偷渡潮持续而令其体面受损,为了阻止广东人民大量偷渡,决定让广东先富起来。最终,中国大陆1970年代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及1980年建立深圳经济特区,优先开放深圳、广州以及珠三角[31]。广州及深圳从此成为中国大陆富有地区,人民生活质素大大提升,再加上香港在1980年实施即捕即解,不再值得冒九死一生之风险偷渡来港。偷渡人潮大量减少同时,亦使其他省份人口大量移居广东[32],深圳最低工资亦是全大陆第一(2013年时达每月1600元),引来各省居民争相到深圳工作[33]。
当时,中国内地政府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曾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其中是如此描述:
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 香港黑社会横行; 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 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由于香港在1997年前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管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如大跃进、上山下乡及文化大革命影响不到香港,香港又处于经济腾飞时期,所以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事实上比中国大陆高出了许多。[35]
当时的饥荒导致云南边境居民偷渡到缅甸加入军阀部队谋生,在延边朝鲜族边民偷渡到北韩。1962年发生伊塔事件,大量新疆人偷渡苏联。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以司徒华为首的香港人士发起黄雀行动,秘密将民运人士营救至香港。北韩人通过各种方法偷渡和移居韩国(或其他地方),他们又被称为“脱北者”。
附录中印人均收入的对比
第3章 危机的解析
1929年中开始的那次经济萧条,对美国来说,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灾难。在1933年,经济降到最低点之前,以美元计算的国民收入减少了一半。总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失业人数上升到劳动力总人数的25%这一空前水平。这次萧条对于世界其他地方也是一场灾难。萧条逐渐扩及到其他国家,各国的产量下降,失业人数增加,人民遭受饥饿和苦难。在德国,萧条帮助了希特勒上台,铺平了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在日本,它加强了那个立志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军人集团。在中国,它导致了货币改革,这种改革最后加速了恶性通货膨胀,注定了蒋介石政权垮台的命运,使共产党上了台。
【按:我国的货币改革失败和当时美国财政部中的苏联间谍比如怀特很有关系!】
在思想上,萧条说服了公众,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注定要经受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公众转向了在知识分子中间已经越来越被接受的看法:政府应起更积极的作用;它应进行干预,抵消无节制的私人企业造成的不稳定;它应充当平衡轮,促进稳定和保证安全。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公众对私人企业和政府的作用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导致了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自那时起到现在的迅速扩大。
萧条也使经济学家的看法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经济的崩溃,动摇了那个长期持有并在二十年代曾得到加强的信念,即货币政策是促进经济稳定的有力工具。经济学家几乎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货币同经济稳定不相干”。二十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了另外一种理论。凯恩斯革命不仅俘虏了经济学专业,也为广泛的政府干预提供了吸引人的论据和处方。
公众和经济学家看法的转变,是由于误解了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却很少有人知道———萧条并不是私人企业失败所造成,而是政府在一个从一开始就被赋予责任的领域里的失败造成的。这个责任,用美国宪法第一款第八节的话来说,就是“铸造货币,调节它与外国货币的价值”。不幸的是,我们将在第九章中看到,政府管理货币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历史上的稀奇事,而且也是今天的现实。
联邦储备系统的起源
1907年10月21日,星期一,大约在一次经济衰退开始之后五个月,纽约市的第三大信托公司聂克波克信托公司开始遇到金融困难。第二天对这家银行的“挤兑”迫使它倒闭(结果证明是暂时的;它在1908年3月恢复了营业)。聂克波克信托公司的倒闭,加速了对纽约市内的后来也对全国其他地方的别的信托公司的挤兑——一次银行的“恐慌”发生了,就象在十九世纪不时发生过的那样。
不到一个星期,全国的银行对这种“恐慌”作出了反应,“限制付款”,也就是宣布它们不再付给要求提取存款的储户以通货。在某些州里,州长或司法部长采取措施,给予限制付款以合法的批准;在其他州里,干脆就容忍这种做法,银行被许可继续开业,尽管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它们违反了州的银行法。
限制付款遏制了银行的倒闭,结束了挤兑风潮。但这给企业带来了严重的不便。它导致硬币通货不足,使木质的分币在私下流通,并使其他暂时的代用品代替合法的货币。在通货最短缺时,得用一百零四美元存款买一百美元通货。恐慌加上限制,直接地和间接地使那次衰退变成了美国当时所经历的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所谓直接地,是指恐慌和限制对信心和有效地经营企业造成的影响,间接地是通过强使货币的数量减少。
不过,衰退的严重阶段为时不长。银行于1908年初恢复付款。几个月之后,经济开始恢复。这次衰退总共只持续了十三个月,而它的严重阶段只拖了大约一半那么久。
这一戏剧性的事件要对1913年通过联邦储备法负大部分的责任,它使得在货币和银行领域采取某些行动在政治上成为必要。在西奥多·罗斯福的共和党政府期内,建立了国家货币委员会,主席是著名的共和党参议员纳尔逊·W·奥尔德里奇。在伍德罗·威尔逊的民主党政府期内,著名的民主党众议员后来成为参议员的卡特·格拉斯重新草拟了该委员会的建议。从那以后,由此产生的联邦储备系统就成了国家管理货币的主要权力机构。
“恐慌”、“挤兑”和“限制付款”这些字眼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为什么它们会产生我们归因于它们的那些深远的影响?联邦储备法的作者又是怎样提议防止同样的事件的?
对一家银行挤兑,就是它的许多储户全都在同一个时间试图“提取”他们的存款。挤兑的发生,是由于有谣言或事实,使储户担心银行偿付能力不足,将不能履行它的义务。因而每个人都试图在存款还没有完全丧失之前把“自己的”钱取出来。
不难理解,为什么挤兑会使得一家偿付能力不足的银行更快地陷于破产。但是为什么挤兑也会给可信赖的和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带来困难呢?答案同英文里的一个最引人误解的字眼——“存入”有关,它被用来指对银行的一种要求权。如果你向一家银行“存入”通货,你往往会认为银行拿了你的钞票,把它们放进银行的保险柜里保存起来,等你来取款。它并不是这样做的。要是这样做的话,银行哪来的收入去偿付开支,去付存款利息呢?银行可能拿一些钞票放到保险柜里作为“储备”。其余的钞票它贷给别人,要借款人付利息,或者用于购买有息证券。
如果你存入的不是通货而是其他银行的支票(人们经常这样做),那么银行手头上就连可存入保险柜的通货也没有。它只有对另一家银行提取通货的要求权,而通常它并不行使这种权利,因为其他银行对它也拥有与此相当的要求权。对每一百美元存款,所有银行只在保险柜里存放几美元现金。我们实行的是“部分储备银行制”。只要人人都相信随时能够从存款中提取现金,因而只在真正需要时才提款,这种制度就能很好地运行。通常,新存入的现金大致与提取额相等,所以那一小部分储备就足以应付暂时的差额。但是要是人人都一下子取回现金,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多半会造成恐慌,就如有人在拥挤的戏院里喊“起火了”,每一个人都会赶紧往外跑一样。
如果只有一家银行碰到挤兑,那它可以从其他银行借款或是要求其借款人归还贷款来对付。借款人可以从别的银行提取现款来偿还贷款。但如果一场银行挤兑风潮扩大,银行是无法共同这样对付挤兑的。在银行的保险柜里干脆就没有那么多的通货,来满足所有储户的要求。此外,动用库存现金来对付广泛的挤兑——除非能立即恢复信任,结束挤兑,从而现金再次被存入银行——会使存款额大为减少。1907年,每一百美元存款,银行平均只有十二美元现金。每一美元存款换成现金从银行的保险柜转到存款人手里,需要另外减少七美元的存款,银行才能保持原来储备金同存款的比率。这就是为什么一场挤兑,结果使公众贮藏现金会减少总的货币供应量的缘故。这也就是为什么挤兑风潮如不立即终止会造成巨大痛苦的缘故。各个银行会催借贷户还债,拒绝延长贷款期限或拒绝发放新的贷款以取得现金,应付储户的要求。借贷户整个地告货无门,于是银行倒闭,企业破产。
如何能在一场恐慌一旦发生时就使之停止,或者更好的是如何能在它开始之前就加以防止呢?制止恐慌的一种办法,是象1907年那样:银行一起限制付款。银行仍然开业,但它们相互约定,储户提款时不付给现金,而是通过转帐来处理。对于自己银行的某一储户开给另一储户的支票,各银行的承兑方法是:减少前者帐下的存款,而增加给后者。对于那些由自己的储户开给其他银行的储户的支票或是由其他银行的储户开给自己银行的储户的支票,它们就几乎象往常那样,“经过票据交换所”来处理,也就是用所收到的其他银行储户的支票,抵消其他银行所收到的自己银行储户的支票。一个区别是,它们要付给其他银行的款项同其他银行要付给它们的款项之间的任何差额,是用支付保证来解决,而不是象通常那样拨付现金。银行也支付一些现金,不过不是付给要求提款的储户,而是付给一些老主顾,以供他们发放工资和其他紧急需要之用,同时银行也从这些老主顾那里得到一些现金。在这种制度下,某些“不殷实的”银行仍然可能倒闭。但它们倒闭,不是因为它们不能把殷实的资产转换成现金。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慌逐渐得到平息,对银行的信任得到恢复,银行又重新付款给提款的储户,而不致引起一系列新的恐慌。这是制止恐慌的颇为严厉的方法,但它确实起了作用。
另外一种制止恐慌的办法,是使殷实的银行能够把它们的资产迅速转换成现金,不是通过损害其他银行来转换,而是通过取得额外的现金——也可以说是通过紧急印刷机来转换。这就是体现在联邦储备法中的方法。据认为,该方法甚至可以防止限制付款引起的暂时混乱。根据该法建立的十二家地区银行,在华盛顿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督下营业,受权充当商业银行的“最后可以求助的放款者”。它们可以发放以下两种贷款,一种是以货币形式发放联邦储备券(它们有权印刷这种储备券),另一种是发放银行帐目上的存款信贷(它们有权创立这种信贷,只要薄记员把大笔一挥就行了)。它们充当银行家的银行。美国的地区银行相当于英格兰银行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
最初,人们预计,联邦储备银行的大部分业务是直接贷款给银行,以这些银行自己的资产,特别是以它们的期票即提供给企业的贷款为担保。但在许多这种贷款上,银行对期票进行“贴现”——也就是付出的款项比面值少,其折扣代表银行收取的利息。联邦储备反过来对期票进行“再贴现”,以此从银行收取贷款的利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开的市场活动”——即买卖政府公债——而不是再贴现,变成了联邦储备系统放松和收紧银根的主要方法。当一家联邦储备银行买进政府公债时,它支付联邦储备券(那是它保险柜里有的或者新印刷的),更通常的办法是,在它的帐本上为一家商业银行增加存款。这家商业银行可以自己是公债出售者,也可以是公债出售者保有存款户头的银行。这些额外的通货和存款就充作商业银行的储备,使它们整个能够成倍地扩大它们的存款,这就是为什么联邦储备银行的通货和存款被称为“高能货币”或“货币基础”的原因。当联邦储备银行售出公债时过程正好相反。商业银行的储备下降。它们被引向收缩。直到不久前,联邦储备银行创造通货和存款的权力,还受到联邦储备系统掌握的黄金量的限制。这个限制现在已被取消,所以今天除了负责这个系统的人的谨慎外,已不再有任何有效的限制。
三十年代初期,联邦储备系统未能做到建立它要做的事情之后,最后在1934年采取了一个防止恐慌的有效方法,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保证存款最大限度地不受损失。该保险公司使存款人相信他们的存款是安全的,因而防止了不殷实的银行的倒闭或金融困难造成对其他银行的挤兑。在那拥挤的戏院里的人们相信,再不会有火灾了。自1934年以来,虽然也曾有过银行倒闭和对个别银行的挤兑,但还没有发生过那种老式的银行恐慌。
早在1934年以前,为了防止恐慌,银行就已经常对存款进行担保了,只不过担保的范围较小,没有那么有效罢了。一次又一次,当一家银行碰到金融困难或是因为谣传发生问题而有挤兑危险时,其他银行就自动联合起来凑集一笔资金,为处于困难中的那家银行的存款担保。这种方法防止和阻止了许多恐慌。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或者是因为没有达成一项满意的协议,或者是因为没有立即恢复信心,该方法却没有奏效。关于这种失败,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考察一个特别富有戏剧性的重要事例。
联邦储备系统的早年
联邦储备系统于1914年底,欧洲爆发世界大战后的几个月,开始活动。这场战争大大改变了联邦储备系统的作用和重要性。
该系统建立时,金融世界的中心是英国。据说,当时世界建立在金本位制上,但同样可以说是建立在英镑本位制上。当初建立联邦储备系统,首先是为了防止银行恐慌并促进商业;其次是充当政府的银行。当时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将在世界金本位制的范围内活动,对国外事件作出反应,而不是去左右它们。
战争结束时,美国取代英国,成为金融世界的中心。世界有效地建立在美元本位制上,而且,即便是在战前的金本位制以一种削弱了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之后,也还是这样。联邦储备系统已经不再是一个被动地对国外的事件作出反应的无足轻重的机构。它已成了一个能够影响世界货币结构的独立的巨大力量。
战争期间,特别是美国参战后,不论是好还是坏,总之,联邦储备系统显示了其巨大力量。象在以前的(和后来的)战争中一样,为了筹措战费,印刷机又被派上了用场。不过,联邦储备系统使用印刷机的手法,要比以前的政府机构更为老练和隐蔽。联邦储备银行向财政部购买债券,用联邦储备券支付,使财政部能用储备券交付一些费用,只有在这时,才在某种程度上真正使用印刷机。在大多数情况下,联邦储备银行向财政部购买债券时,只是在帐册上给后者记一笔存款,以此作为付款。财政部用这些存款的支票支付它购买的东西。当支票接受人把支票存到他们自己的银行时,这些银行又把它们存到联邦储备银行,这样,财政部在联邦储备银行的存款就转给了商业银行,增加了它们的储备金。储备金的增加,使商业银行系统得以不断扩充,这种扩充在当时主要是通过它们自己购买政府公债或是贷款给它们的主顾使他们能够购买公债取得的。用这种办法,财政部得到了新创造出来的货币来支付战费,但增加的货币大都以商业银行存款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通货的形式出现。采用这种方法巧妙地增加货币数量,并没有防止通货膨胀,但它确实有神不知鬼不觉的作用,掩盖了实际发生的情况,减少或是延缓了公众对通货膨胀的担心。
战争结束以后,联邦储备系统继续迅速增加货币数量,从而助长了通货膨胀。但是在这一阶段,增加的货币不是用于政府开支,而是用于资助私营企业活动。我们整个战时的通货膨胀,有三分之一是发生在不仅战争结束而且政府的战争开支赤字也已结束之后。联邦储备系统很晚才发现它的错误。发现后,马上作出了强烈反应,把国家投入了1920-1921年为时不长但很严重的萧条。
无疑,联邦储备系统取得最大成功的时代,是在二十年代剩下的那段时间里。在那些年,它的确象一个有效的平衡轮似的起作用,当经济显露出摇摆的迹象时就提高货币的增长率,当经济开始以较快的速度扩张时就降低货币的增长率。它并没有使经济免于波动,但它的确缓和了波动。不仅如此,它是不偏不倚的,因而避免了通货膨胀。货币增长率和经济形势的稳定,使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当时有人大肆鼓吹说,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商业周期完蛋了,被一个警觉的联邦储备系统排除了。
【按:此时被称为“柯立芝(Coolidge)繁荣”,柯立芝执政策略:减税、降低政府开支、减少监管、加关税。由加关税可以看出美国并不是什么自由贸易的代表。】
二十年代的成就,大都应归功于一位名叫本杰明·斯特朗的银行家。此人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第一任行长,一直到1928年他突然病故时为止。在他死以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可以说是联邦储备系统执行的国内外政策的主要推动者,而本杰明·斯特朗无疑是最最关键的人物。他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正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所描述的,是“一个天才——银行家中的汉密尔顿”。同联邦储备系统内的其他人相比,斯特朗得到了该系统内部和外部金融界领袖们的更多信任和支持,他能够使金融界的领袖们相信他的看法,而且他有勇气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干。
斯特朗的死在联邦储备系统内部引起了权力之争,这场斗争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果。正如斯特朗的传记作者所说,“斯特朗的死使联邦储备系统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它失掉了一个有胆有识、深孚众望的领导人。〔设在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不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起那个作用。但该委员会自己又不能大胆地发挥那个作用,它当时仍然是软弱和分裂的……而且其他联邦储备银行大都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一样,不愿接受该委员会的领导。……因而,该系统陷入了遇事作不出决断、各方意见僵持不下的困难境地。”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权力之争竟然大大加速了权力转移,权力从私人市场转给了政府、从地方和州政府转给了联邦政府。事实证明,这场权力之争是权力转移的第一步。
萧条的开始
流行的看法是,大萧条开始于1929年10月24日。那天是星期四,天阴得非常厉害,纽约的证券市场崩溃了。其间经过几上几下,最后证券价格在1933年跌落到1929年那令人眩目的水平的六分之一。
证券市场的崩溃固然重要,但它并不是萧条的开始。企业活动在1929年8月,即证券市场崩溃前两个月就已达到了其顶峰,到10月时已经大大减少了。崩溃反映了经济困难的不断增加,反映了无法维持的投机活动的破产。当然,一旦发生崩溃,它就会在企业界人士和其他曾对新时代的到来寄予无限希望的人们中间散布疑虑。它使消费者和企业经营者都不愿花钱,而希望增加他们的流动储备以备急需。
联邦储备系统随后的做法,更加重了证券市场崩溃所造成的影响,危机进一步加深。当崩溃发生的时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几乎是出于斯特朗时代养成的条件反射,立即自行买进政府公债从而增加银行的储备,来缓和冲击。这使商业银行能够向证券市场上的公司提供额外的贷款,并从它们那里和其他受到崩溃的不利影响的公司那里买进证券,以缓和冲击。但是,斯特朗已经死了,联邦储备委员会想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它迅速行动,要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遵守纪律,后者屈服了。此后,联邦储备系统的做法就同它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早先的经济衰退中的做法大不一样了。它不是积极放松银根,使货币供应量多于平时,以抵消收缩,而是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听任货币数量慢慢减少。在1930年末到1933年初这段时间里,货币数量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一,与此相比,1930年10月前货币数量减少的幅度仍显得很小,仅仅减少了2.6%。不过同已往相比这个幅度却很大。的确,同以前的衰退相比,不论是在衰退期间还是在衰退之前,几乎哪一次货币也没有减少这么多。
证券市场崩渍的余波和1930年间货币数量的缓慢减少,最终导致了一场相当严重的衰退。即使那次衰退在1930年末或1931年初就告结束——如果不是发生货币崩溃的话,它本来很可能会是那样——它也会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衰退。
银行业的危机
但是,最坏的情况还在后头。直到1930年秋天,收缩虽然严重,但还没有发生银行业的困难或向银行挤兑的情况。当中西部和南部一系列银行倒闭破坏了人们对银行的信心并使人们广泛地想把存款变成通货时,衰退的性质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银行倒闭的浪潮最后蔓延到了全国的金融中心纽约。1930年12月11日是个非常关键的日子,那一天美国银行关了门。这是直到那时为止美国历史上倒闭的最大一家商业银行。此外,虽然它是一家普通的商业银行,它的名称却使国内外许多人认为它是官方银行。因而它的倒闭是对信心的特别严重的打击。
美国银行能起这样的关键性作用,是有几分偶然因素的。由于美国银行业的结构分散,加上联邦储备系统采取的政策是让货币储藏量减少而且不对银行倒闭作出有力反应,所以小银行的倒闭迟早会造成对其他大银行的挤兑。即使美国银行不倒闭,也会有其他大银行来诱发雪崩似的银行倒闭浪潮。是美国银行而不是其他银行倒闭,纯粹是偶然的巧合。它是一家殷实的银行。尽管它是在萧条最严重的几年里被清算的,但最后还是为每一美元存款偿付了九十二点五美分。无疑,如果它当时能挺住,储户一分钱也不会损失的。
当关于美国银行的谣言开始传播的时候,纽约州的银行总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纽约票据交换所银行协会曾试图制定一个计划挽救这家银行,为它提供保险基金或使它同其他银行合并。这是早先发生恐慌时标准的做法。直到银行关闭前两天,人们还认为这些努力一定能成功。
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了,主要是因为美国银行的特点加上银行界的偏见。它的名称本身,因为吸引移民,所以为其他银行所忌恨。更为重要的是,这家银行是犹太人拥有和经营,并主要是为犹太人服务的。它是在这一行业里少数几家犹太人拥有的银行之一,这个行业比几乎任何其他行业都更加照顾达官贵人。救助计划包括使美国银行同唯一另外一家纽约市内主要为犹太人所有和经营的大银行以及两家小得多的犹太人拥有的银行合并,不是偶然的。
计划失败是因为纽约票据交换所在最后一刻退出了所提议的安排——据说主要原因是一些银行界头面人物的反犹主义。在银行家们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纽约州银行总监约瑟夫·A·布罗德里克曾试图说服他们,但没有成功。他后来在法庭审讯时作证说,
“我当时说,它(美国银行)有许许多多借款人,它资助小商人,特别是犹太商人,它的关闭可能会使大批储户和借户破产。我警告说,它的关闭会使市内至少另外十家银行关闭,还可能影响储蓄银行。我告诉他们,关闭的影响甚至可能超出本市的范围。
我提醒他们,不过两三个星期以前,他们还拯救过市内两家最大的私人银行,曾经愿意提供所需要的资金。我回忆说,不过七、八年前,他们曾帮助过纽约的最大一家信托公司,提供的资金比拯救美国银行所需的数目要多许多倍,不过只是在制止了他们一些人之间的争吵之后。
我问他们,他们放弃这个计划的决定是否仍然不可更改。他们告诉我是这样。于是我警告他们,说他们正在犯纽约银行业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
美国银行关门,对它的所有人和储户来说都是悲剧。两个所有人受到审讯,据说违反了法律而被判处徒刑。储户的钱虽然最后得到部分偿还,但却被扣押了好多年。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后果更为深远。全国各地的存款人担心他们存款的安全,加入了早先已经开始的零星的挤兑活动。银行成批倒闭,仅1930年12月一个月,就有三百五十二家银行倒闭。
如果没有建立联邦储备系统,而发生挤兑风潮,那么,毫无疑问,银行会采取1907年采取过的措施,即限制付款,这种限制会比1930年最后几个月实际实行的要严厉得多。但是它会防止银行储备金的流失,几乎一定会防止后来1931、1932和1933年的银行大倒闭,正如1907年的限制很快就制止了当时的银行倒闭一样。的确,如果真是那样,美国银行也许会重新开业,就象聂克波克信托公司在1908年那样。恐慌过去,信心恢复,经济很可能在1931年初就开始复苏,就象在1908年初那样。
联邦储备系统的存在阻止了银行采取这种激烈的治疗措施:直接地是因为大银行的担心减少了,它们相信向联邦储备系统借钱可以使它们克服可能发生的困难,事实证明它们错了;间接地是因为整个社会特别是银行界相信,现在有联邦储备系统对付挤兑风潮,再不需要采取这种严厉的措施了。
联邦储备系统本来可以提供好得多的解决办法,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买进政府公债。这将为银行提供额外的现金以应付它们储户的要求。这会制止大批银行倒闭,至少是急剧减少倒闭的银行数目,防止公众把存款换成通货,从而不致使货币数量减少。不幸的是,联邦储备系统犹豫不决,采取的行动很少。总的来说它是袖手旁观的,听凭危机自由发展——在后来的两年中,它一再重复这种行动方式。
1931年春天,当第二次银行业危机来临时,联邦储备系统就是这样行事的。1931年9月,当英国放弃金本位制时,它甚至采取了更为反常的政策。联邦储备系统的反应是——在发生严重萧条两年以后——前所未有地大幅度提高利率(贴现率)。它采取这个行动是为避免持有美元的外国人来汲取它的黄金储备,这是它担心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提高利率,结果使国内的通货高度收缩——给商业银行和工商企业更增加了压力。联邦储备系统本来可以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政府公债,来抵消它给予正在挣扎的经济的这一剧烈打击,但它没有那么做。
1932年,在国会的强大压力下,联邦储备系统最后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买进债券。有利的影响刚开始被感觉到,国会休会了,而联邦储备系统立即就停止了它的计划。
这一惨痛故事的最后一段是1933年银行业的恐慌,又一次以一系列的银行倒闭开始。胡佛和罗斯福之间的交接班更加重了这次恐慌。罗斯福于1932年11月8日当选,但到1933年3月4日才就职。胡佛不愿意在未得到新当选总统合作的情况下采取严厉措施,罗斯福不愿意在他就职以前承担任何责任。
恐慌在纽约金融界蔓延开来,联邦储备系统自己也慌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试图说服胡佛总统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天宣布全国银行休假,但没有成功。他于是就会同纽约票据交换所银行和州的银行总监,说服纽约州长莱曼宣布全州各家银行在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职那一天休假。联邦储备银行与商业银行一起停业。其他州的州长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最后罗斯福总统在3月6日宣布全国休假。
中央银行系统的建立,最初是为了使商业银行无需限制付款,但后来它却同商业银行一道,对银行付款实行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无比广泛和完全的限制,严重地扰乱了经济。人们一定会赞同胡佛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的这样一句话:“我的结论是,它(联邦储备委员)在全国发生困难的时候,的确是一根不中用的稻草。”
在1929年中期经济处于顶峰时,美国有近二万五千家商业银行开业。到1933年早期,减少到了一万八千家。在罗斯福总统于银行休假开始十天后宣布其结束时,只有不到一万二千家银行获准开业,后来也只增加了三千家。因此,在四年的时间里,由于倒闭、合并或清算,在二万五千家银行中,总共大约消失了一万家。
货币的总量也同样急剧减少。如果1929年公众手头的存款和通货为三美元的话,那么到1933年就只剩下了不到两美元,真可以说是一次空前的货币崩溃。
事实和解释
这些事实今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事情,不过应当强调指出,当时的大多数观察家却没有看到这些事实,包括约翰·M·凯恩斯在内。人们可以对这些事实作不同的解释。货币崩溃是经济崩溃的原因呢还是结果?是联邦储备系统本来应该能够防止货币崩溃,还是象当时许多观察家得出的结论那样,联邦储备系统已经作了最大努力,但货币崩溃仍然不可避免?萧条是在美国开始然后扩及到国外呢,还是发源于国外而把美国国内本来可能是颇为温和的衰退加重了?
原因或结果
联邦储备系统本身对自己的作用没有任何怀疑。联邦储备委员会竭力为自己辩护,竟然在它的1933年《年度报告》中大言不惭地说:“联邦储备银行能够应付危机期间对通货的巨大需求,这显示了我国根据联邦储备法建立的货币制度的效能。……要不是联邦储备系统在公开市场上自由地购进债券,很难说萧条会怎么发展。”
货币崩溃既是经济崩溃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货币崩溃主要是联邦储备政策的,而它无疑加重了经济崩溃。经济崩溃一旦开始,又使货币崩溃恶化。银行贷款,在比较温和的衰退时期可能是“好的”贷款,但到了严重的经济崩溃时,就变成“坏的”贷款了。拖欠偿付贷款,削弱了发放贷款的银行,更促使存款人开始向它挤兑。企业倒闭,产量下降,失业增加——都加重不放心和担忧的感觉。把资产变换成其最流动的形式货币,变换成最保险的货币通货,成了广泛的愿望。“反馈”是经济制度的普遍特征。
现在,几乎已可确证,联邦储备系统不仅被授权防止货币崩溃,而且要是它把联邦储备法赋予它的权力运用得当的话,本来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这个系统的卫护者提出了一系列的借口。但其中没有一个经得起仔细推敲。没有一个足以说明,这个系统没有能完成它的创始人建立它所要完成的任务,是有道理的。联邦储备系统不仅有力量防止货币崩溃,而且也知道如何运用这个力量。在1929、1930和1931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曾反复敦促联邦储备系统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购进债券,这是联邦储备系统本应采取的关键性行动,但它没有采取。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并不是因为这些建议不对头或行不通,而是因为系统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得其他联邦储备银行和联邦储备委员会都不愿意接受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领导。结果只得受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混乱而犹豫不决的领导。该系统以外的有识之士也曾要求采取正确的行动。伊利诺斯州的议员A.J.萨巴思在众议院说:“我认定,解除金融和商业的困苦是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范围内的事。”某些提出批评的学术界人士——包括卡尔·鲍勃,他后来成为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在一次联邦储备会议上——这次会议在国会的直接压力下批准了1932年的公开市场购进——当时的财政部长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奥格登·L·米尔斯在说明他赞成那个行动时指出:“一个拥有70%黄金储备的大中央银行系统,在这样的形势下站在一边,不采取积极步骤,这几乎是不可想像、几乎是不可饶恕的。”然而这恰恰就是这个系统前两年的做法,而且在几个月后国会刚一休会以及在1933年3月最后银行危机达到高潮时,他又采取了这种做法。
萧条从哪里开始
萧条是从美国扩及世界其他地方而不是相反,这可以从黄金的流动情况得到肯定的证明。1929年,美国实行的金本位制规定了黄金的官价(每盎司二十美元六十七美分),按照这个价格,美国政府将应要求买进或售出黄金。多数其他大国实行的是所谓金汇兑本位制,它们也给黄金规定按它们自己的通货计算的官价。用美国的官价除以按它们的通货规定的黄金官价,便得出官方兑换率,也就是以美元表示的它们通货的价格。它们可以按照也可以不按照官价自由买卖黄金,但他们负责把汇率保持在按这两种黄金官价确定的水平,需要时按这个兑换率买进和售出美元。在这种制度下,如果美国的居民或其他持有美元的人在国外花费(或借出或赠送)的美元,比接受这些美元的人愿意在美国花费(或借出或赠送)的多,那么,后者就会用多余的美元兑换黄金。黄金就将从美国流向外国。如这差额是相反方向的,持有外国通货的人想在美国花(或借出或赠送)的美元,比持有美元的人愿意兑换外国通货在国外花(或借出或赠送)的多,那么,他们可以向他们的中央银行按官定兑换率购买额外的美元。他们的中央银行将把黄金送到美国以得到这额外的美元。(当然,实际上这种交换并不需要真的远渡重洋运送黄金。外国中央银行拥有的黄金,有许多就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金库里,加有所属国家的“标记”。转换的时候只要改变华尔街地区自由大街33号银行大楼地下室深处盛放金条的容器上的标签就行了。)
如果萧条是起于国外,而美国经济在一段时间里继续繁荣,那么,国外恶化的经济情况会减少美国的出口,而外国货的价钱降低,会鼓励美国进口。结果会是想在国外花(或是借出或赠送)的美元,要比接受者想在美国花的多,这样黄金就从美国流出。黄金的流出会减少联邦储备系统的黄金储备,从而促使联邦储备系统减少货币数量。固定汇率制就是这样把通货收缩(或通货膨胀)的压力从一个国家转移给另一个国家的。如果当时情况是这样,那么联邦储备委员会会理直气壮地说,它的行动是为了对付外来压力的。
反过来,如果萧条起于美国,那么最初的影响就会是持有美元的人想在国外花的美元数目减少,而其他人想在美国花的美元数目增加。这会使黄金流进美国,从而迫使外国减少它们的货币数量,这样,美国的通货收缩就转移给了外国。
事实是清楚的。从1929年8月到1931年8月,即通货收缩的头两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增加。这确凿地证明,美国是萧条的发动者。如果联邦储备系统遵循金本位制的原则,那它应当增加货币的数量来对付黄金的流入。相反,它实际上却听凭货币的数量减少。
一旦萧条发生并传给其他国家,自然就会对美国产生反作用。这是又一例证,说明复杂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着反馈作用。处在一场国际运动前列的国家,并不一定永远处在前列。法国1928年重新实行金本位制后,所规定的兑换率使法郎贬值,因而积聚了一大笔黄金。所以它完全能够抵挡来自美国的通货收缩的压力。可是法国执行了甚至比美国还严厉的通货紧缩政策,不仅开始增加它的本来已经很多的黄金储备,而且,从1931年末起开始从美国收购黄金。它发挥这种领导作用所得到的报酬是,虽然美国经济在1933年3月降到最低点,停止支付黄金,法国的经济却直到1935年4月才达到最低点。
对联邦储备系统的影响
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好心劝告而执行反常的货币政策,其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之一是,在同纽约和其他联邦储备银行争权的斗争中,该委员会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当时流传的神话是:私人企业包括私人银行系统失败了,政府需要更多权力以对付据说是自由市场固有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储备系统的失败,产生了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得以对地区银行进行更多的控制。
这种变化的象征之一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从美国财政部大楼里的朴素的办公处迁到了宪法路它自己的一座堂皇的希腊庙宇里(从那以后又加建了巨大的建筑)。
这场权力转移的最后一个标志是,改变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名称和地区银行负责人员的称号。在中央银行圈子里,受尊敬的称号是行长而不是总经理。从1913年到1935年,地区银行的头头称作“行长”;华盛顿的中央机构叫作“联邦储备委员会”,只有该委员会的主席称“行长”,其他成员就叫“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1935年的银行法把这些都改了。地区银行的头头不再叫“行长”,改叫“总经理”,而“联邦储备委员会”这个紧凑的称呼改成了臃肿的“联邦储备系统行长会议”,只是为了使每一个成员都有“行长”称号。(译注:“联邦储备系统行长会议”的习惯译法是“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总经理”亦译“行长”。这里为了便于看清其(改变的意义,故改成以上译法。)
不幸,增加权力、威望和办公处的装璜并没有相应改善工作。自1935年以来,这个系统主持了——而且大大促进了——1937-1938年的大衰退、战时和战后的通货膨胀以及从那时以来起伏不定的经济,通货膨胀时高时低,失业时增时减。每一次通货膨胀的高峰和每一次暂时的通货膨胀低落点。都一次比一次高;平均的失业水平也逐渐升高。该系统没有再犯它在1929-1933年犯的那种错误——容许或促进一场货币崩溃——但它犯了相反方面的错误,促使货币数量过分迅速地增加,这就助长了通货膨胀。此外,它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不仅制造景气,而且也制造不景气,有些是温和的,有些是剧烈的。
该系统只在一个方面完全保持始终如一。它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非它所能控制的外部影响,而把所有有利的情况都归功于自己。它就是这样继续助长那个说私人经济不稳定的神话,而它的行为则继续证明这个现实:政府是今天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本节内容概述
本节回顾美联储的早期历史,证明美联储是美国大萧条的罪魁祸首。
该系统只在一个方面完全保持始终如一。它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非它所能控制的外部影响,而把所有有利的情况都归功于自己。它就是这样继续助长那个说私人经济不稳定的神话,而它的行为则继续证明这个现实:政府是今天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附录:中国货币改革失败和美国、苏联的关系
1953年真纳和麦卡锡的指控
参议院威廉·真纳领导的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SISS)对政府部门进行的内部连环彻查中对非民选官员行使未经授权和不受控制权力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调查,特别是针对怀特。得出报告中的部分是关于罗斯福政府施行的中国政策,以《摩根索日记(中国)》为名出版。报告称:
“财政部中特别是财金研究部里聚集了大量共产党同情者,这是创下纪录的事实。怀特是该部门的第一任主管,继承他的主管是柯福兰和哈罗德·葛莱瑟。受雇于财金研究部的有威廉·路德维格·乌尔曼、厄尔文·卡普兰和维克托·佩洛。其中,怀特、柯福兰、葛莱瑟、卡普兰、佩洛都被认定为共产党阴谋组织的成员……”
委员会还听取了亨利·摩根索的演讲撰写人乔纳森·米歇尔的证词,指出怀特试图说服他苏联已经发展出一套可以取代资本主义和基督教的体系。
1953年,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司法部长小赫伯特·布朗内尔公布了在杜鲁门总统任命怀特任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联邦调查局给政府当局发出的警告。布朗内尔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5年11月8日写给白宫的信,其中对怀特及其他人发出了警告。这显示白宫在杜鲁门提名怀特任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六周之前就已收到联邦调查局题为《苏联在美间谍活动》的报告,其中就包括怀特的案件。
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在1997年莫伊尼汉委员会报告中就政府保密问题写下的引言中,尽管不否认联邦调查局向杜鲁门发出许多此类警告,但指出杜鲁门始终未被告知关于维诺那计划的情况。为证明此点,他引用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撰写的维诺那计划官方历史中的一则声明称“没有明显证据能够证明”杜鲁门总统知晓维诺那计划。
维诺那计划
国安局的密码学家认定哈里·迪克特·怀特就是维诺那计划破解密电多次提到的消息来源,其行动代号有“律师”、“理查德”和“陪审员”。在他死后两年,在一份1950年10月15日成文的备忘录中,怀特被联邦调查局根据维诺那计划收集的证据认定为苏联线人,行动代号“陪审员”。
数年后,司法部公开了维诺那计划,其中破解的苏联有线电报里以“陪审员”指代苏联线人怀特。联邦调查局就怀特提交的备忘录中报告称:
“您此前已经收到从(维诺那计划)中搜集到的关于‘陪审员’的情报,此人活跃于1944年。根据(维诺那计划)之前收到的关于‘陪审员’上交的情报,1944年4月间他提交了关于时任国务卿赫尔同副总统华莱士之间对话的报告。他还报告了华莱士的中国之行。1944年8月5日他向苏联报告称他坚信除非有一场重大军事失利,罗斯福能够在即将到来的的选举中获胜。他还报告说选择杜鲁门担任副总统是考虑到要保证民主党保守派的选票。据报告称,‘陪审员’很愿意为克格勃做出任何个人牺牲,但他担心他的行为一旦曝光会造成政治丑闻,对选举会有影响。”
这一代号被克格勃档案员瓦西里·米特罗欣的笔记证实,其中点出了六名关键性苏联特工的名字。哈里·迪克特·怀特位列其中,其代号一开始是“卡西尔”后来是“陪审员”。
怀特作为帮助苏联发挥影响力的特工的另一个例子就是他在1943年阻挠了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一笔已许诺的两亿美元贷款,他所收到的指令要求在通货膨胀上升至不可控制之时就要执行这笔贷款。
另一些维诺那破解密电显示出对怀特更加不利的证据,包括怀特向他的苏联递信人建议如何碰头和传递信息。维诺那档案71号破解密电包含了怀特讨论为他给苏联所做工作应得的报酬。
1997年,由民主党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担任主席的跨党派有关政府保密事务的莫伊尼汉委员会公布其结论:“关于国务院的阿尔杰·希斯的复杂案件已经可以定案,财政部的哈里·迪克特·怀特亦是如此。”
苏联档案员和克格勃工作人员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披露了关于怀特充当苏联特工行为的复杂性的更多证据。在其与阿兰·韦恩斯坦所著的《闹鬼的森林:苏联在美间谍活动——斯大林时代》(The Haunted Wood: Soviet Espionage in America — the Stalin Era)中,作为前苏联记者和克格勃工作人员的瓦西里耶夫公布了关于怀特为苏联做事的相关苏联档案。怀特坚持把财政部职员、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间谍哈罗德·葛莱瑟“提拔并保留在财政部,尽管知晓他的共产党背景”。有怀特撑腰,葛莱瑟通过了联邦调查局背景调查。1941年12月秘密情报部门向哈里·怀特提出报告指出有证据表明葛莱瑟参与了共产党活动。怀特从未回应这份报告。葛莱瑟继续供职于财政部,很快开始招募其他特工,并开始给苏联内政部提供有关财政部人员和其他潜在间谍人选的简报。在美国参加二战以后,葛莱瑟在怀特的批准下得以得到政府部门中几个更高职位的任命。
根据苏联档案,怀特的其它克格勃代号有“理查德”和“里德”。为了保护这一线人,苏联情报部门经常更换怀特的行动代号。
附录: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第一代凯恩斯男爵(John Maynard Keynes, 1st Baron Keynes,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一般称作凯恩斯(或译为凯因斯),英国经济学家。
凯恩斯一反自18世纪亚当·斯密以来尊重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预的经济学思想,他主张政府应积极扮演经济舵手的角色,透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对抗经济衰退乃至于经济萧条。
凯恩斯的思想不仅是书本里的学说,也成为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世界性经济萧条时的有效对策,以及构筑起1950年代至1960年代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繁荣期的政策思维,因而被夸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或译救世主)”、“战后繁荣之父”等。一度主宰资本主义的凯恩斯思想也成为经济学理论与学派之一,称为“凯恩斯学派”,并衍生数个支系,其影响力持续至今。
凯恩斯可谓经济学界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发表于1936年的主要作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起了经济学的革命。这部作品使人们对经济学和政府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凯恩斯发展了关于生产和就业水平的一般理论。其具有革命性的理论主要是:
- 关于存在非自愿失业条件下的均衡:在有效需求处于一定水平下的时候,非自愿失业是可能的。与古典经济学派相反,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无法解决非自愿性失业问题。
- 引入不稳定和预期性,建立流动性偏好倾向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投资边际效应概念引入推翻了萨伊定律和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
他的这些思想为政府干涉经济以摆脱经济萧条和防止经济过热提供了理论依据,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凯恩斯一生对经济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曾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不过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的政策也带来停滞性通货膨胀,因此也称他为“战后滞胀病之父”。
新凯恩斯学派是20世纪50、60、70年代时,部分经济学家为应对第一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挑战而提出的。差异有以下二点:
- 保罗·萨缪尔森等新凯恩斯学派学者把国家干预不只视为为应对经济危机的应急措施,而当作调节经济的基本手段,主张在萧条时采用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在繁荣时采用紧缩性政策抑制经济,以求让经济平稳发展。
- 新凯恩斯学派除了凯恩斯学派一様重视财政政策外,也主张同时调整货币政策,以对经济的刺激更为有力。
新兴凯恩斯学派是劳伦斯·鲍尔、格里高利·曼昆、戴维·罗默、奥利维尔·布兰查德、乔治·阿克洛夫、珍妮特·耶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时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经济出现了“滞胀”现象,新凯恩斯学派由于无法解释该现象受到了怀疑,因此经济学家们提出了新兴凯恩斯学。主要特色是基于工资粘性和价格粘性展开分析,它假设名义工资和产品价格是可以调整的,但是调整速度十分缓慢。
虽然凯恩斯经常被视为热衷于改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社会主义者,他曾表达对资本主义的失败可能会迫使公众转向社会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一事的担忧,而且凯恩斯的一些作品表达了他对改革资本主义制度一事的期望和对于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反感,他曾多次抨击马克思社会主义丶 表示他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荒唐的和乏味的,它从未合理地解释为何会出现经济动荡,而且除了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之外,它从未提出任何有效的建议,并且声称《资本论》是过时的、错误的和毫无用处的,这些言论表明凯恩斯从未认真地审视过马克思的思想,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简化为只主张让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的地位的马克思社会主义以对其进行稻草人论证,但是经济学家加里·蒙吉奥维(Gary Mongiovi)教授认为凯恩斯事实上并不拥护资本主义,而是希望以自由社会主义来取代其地位,但凯恩斯对将来社会的设想是否属于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仍有很大的争议性,而且不像不少反共产主义者所描述的那样,凯恩斯本人十分反对斯大林主义。经济学家爱德华·富勒(Edward W. Fuller)研究了与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有关的文献,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 凯恩斯本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
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及芝加哥派人士曾经公开抨击凯恩斯主义。拥护放任自由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亨利·赫兹利特曾经声称凯恩斯在其著作《通论》中所提出的理论没有一个是真实而原创的。
与凯恩斯的理念相对,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前者的论点都是错误、具有误导性的,他指出凯恩斯的理论仅仅在特殊情况下才能成立。例如,凯恩斯假设货币的周转速度是一定的,个人或企业短期内无法加以改变此宏观经济。而熊彼特指出所有现实迹象都与这种假设相反。时至今日所试行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不管是原始的凯恩斯主义还是被弗里德曼修正了的凯恩斯主义,都已经被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击败。再例如,凯恩斯认为通过操纵几个简单的货币关键因素—政府开支,利率,信贷量或货币流通量就可能维持就业水平和经济繁荣稳定的永久性均衡,但熊彼特的认为符号经济作为主导经济的出现 ,反而打开了通向专制的大门。另外,熊彼特还将凯恩斯所忽略的经济体系“外面”的“边缘”的因素“创新”,作为经济体系真正的核心因素来对待。两位20世纪最负盛名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在经济原理及政治观点上皆可见一斑。
凯恩斯经济学(英语:Keynesian economics),或凯恩斯主义(英语:Keynesianism),凯恩斯理论(英语:Keynesian theory),是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政府应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透过增加总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总体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总体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凯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总体经济学,与以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个体经济学相区别。
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自动机制。这与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依定律相对,后者认为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试图将总体经济学和个体经济学联系起来的努力成了凯恩斯《通论》以后经济学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一方面个体经济学家试图找到他们思想的总体表达,另一方面,例如货币主义和新兴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试图为凯恩斯经济理论找到扎实的个体基础。二战以后,这一趋势发展成为新古典主义综合。
第4章 从摇篮到坟墓
1932年的总统选举是美国政治上的分水岭。争取再次提名为共和党候选人的赫伯特·胡佛面临着严重的萧条问题。数百万人失业。排队领取救济食品,失业者站在街头卖苹果,成了这一时期的标准写照。虽然责任是在独立的联邦储备系统,是它的错误的金融政策使衰退变为灾难性的萧条,然而,作为一国元首的总统,也不能推卸责任。公众丧失了对整个经济体制的信心。人们感到绝望,需要得到一个能够摆脱困境的保证。
民主党候选人是具有超凡魅力的纽约州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作为一位新人,他洋溢着希望和乐观情绪。果然,他按老章程竞选,许诺说要是他当选,将解决政府的浪费,平衡预算,并指责胡佛政府开支无度,听任国家赤字上升。另外,在选举前和就职前的交接班期间,罗斯福经常在奥尔巴尼的州长官邸与他的一伙被称为“智囊”的顾问们碰头。他们制定了罗斯福就职后要执行的措施,后来就形成罗斯福在接受民主党候选人提名时,向美国人民保证要奉行的“新政”。
1932年的总统选举,仅仅就其政治意义来讲,也堪称为分水岭。在1860至1932年的七十二年中,共和党执政五十六年,民主党十六年。在1932到1980年的四十八年中,纪录颠倒了过来,民主党执政三十二年,共和党十六年。
这次总统选举还在一种更为重要的意义上是分水岭。它标志着在公众眼中政府应有的作用和实际上赋予政府的作用的巨大变化。其变化之大可从一组简单的统计数字中看出。自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到1929年,各级政府的开支(包括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除遇重大战事,从未超过国民收入的12%。而且,其中三分之二是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联邦的开支通常只占国民收入的3%或更少。然而,自1933年起,政府开支从未低于国民收入的20%,而目前已超过40%,其中三分之二是联邦政府的开支。不错,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冷战或热战中度过的。然而自1946年以来,光是非国防开支就从未低于国民收入的16%,目前大约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仅联邦政府开支一项就已超过国民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而光是非国防开支就已超过五分之一。靠这种方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联邦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扩大了大约十倍。
罗斯福是在1933年3月4日,即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刻就任总统的。许多州宣布了银行停业。罗斯福就职两日后,下令关闭全国所有银行。但是,罗斯福借就职演说的机会,向全国发表了一篇鼓舞人心的演说。他说:“我们唯一该恐慌的是恐慌本身。”接着。他就发起了一场狂热的立法活动,即所谓国会特别会议“一百天”。
罗斯福的智囊团的成员,主要来自大学,特别是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反映了在这以前已经在校园内的知识分子中间发生的变化,即从信仰个人负责、自由放任和权力分散的、有限的政府,转到信仰社会负责和集权的、强有力的政府。他们认为,政府的职能在于保护个人不受不测风云的影响,并根据“总的利益”来控制经济活动,即便是需要政府来拥有和运用生产资料也罢。这两条原则,早在爱德华·贝拉米1887年发表的著名小说《回顾》中就已提出来了。在那个乌托邦式的幻想小说中,有一位叫里普·范·温克的人物。他一觉从1887年睡到2000年,醒来时发现世界变了样。在“回顾”时,他的新同伴们向他解释了那个令他吃惊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预言的日期——的乌托邦是怎样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苦难中出现的。那个乌托邦就包括了许诺“从摇篮到坟墓”(我们第一次碰上这个词)的保险,以及详尽的政府计划,其中有一规定,所有的人有义务为国家服务一段时间。
【原书按:应该把出现这些词语的整个句子引录下来,因为它十分精确地描述了我们正在走的道路,并无意中暗示了由此造成的后果。原话是这样说的:“再也没有人为自己的未来或是儿女的未来担心了,因为国家为每个公民一生担了保,他们将得到良好的抚养和教育并将过舒适生活。”爱德华·贝拉米:《回顾》(纽约:现代丛书公司,1917年;1887年第1版),第70页。】
罗斯福的顾问们都来自知识界,因而自然把这次萧条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并认为,政府,特别是中央集权政府的积极干预才是对症良药。仁慈的政府官员和无私的专家们,应当从狭隘、自私而又“保守的实业界巨头”手里接管他们滥用的权力。用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的话来说,“货币兑换商从我们文明圣殿的宝座上逃走了。”
顾问们在制定罗斯福的纲领时,不仅能从校园中,而且还从过去俾斯麦的德国、费边的英国和介乎于二者之间的瑞典的经验中得到借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产生的“新政”,明显地反映了这些观点。它包括一些旨在改革基本经济结构的计划。有些计划在最高法院宣布它们为非法之后不得不放弃,最明显的是放弃了建立国家复兴署和农业调整署的计划。其他计划则照旧执行:建立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在全国规定了最低工资限额。
“新政”还包括一些灾祸保险计划,主要有社会保险(老年和遗属保险)、失业保险和政府补助。本章将论述这些措施及其后果。
“新政”还包括一些完全临时性的计划,以对付大萧条带来的紧急情况。这些计划既然是政府计划,因而毫不奇怪,其中一些临时性计划后来就变成了永久性计划。
【按:政府临时执行的紧急性政策应设定一个相对明确的结束时间或标准,例如军政、训政,又如作为临时性措施的九品中正制和两税法。】
最重要的临时性计划有:“创造就业机会”(该计划由工程进度管理署执行),利用失业青年改善国立公园和森林(该计划由地方资源养护队执行),以及联邦政府直接向贫困者提供救济。这些计划的确发挥了作用。当时人们的情绪普遍都很沮丧,迅速采取某种行动来消除这种情绪,帮助陷于苦难中的人们并恢复公众的希望和信念,是重要的。这些计划制定得很仓促,无疑是不完善、不经济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罗斯福政府在消除当时的沮丧情绪和恢复公众信任方面,颇有成效。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新政”,但同时大大加强了它的基础。战争带来了庞大的政府预算以及政府对具体经济生活的前所未有的控制:通过法令规定物价和工资,实行消费品配给,禁止某些民用品的生产,分配原料和成品,以及控制进出口。
失业现象的消灭,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军火库”的战争物资的大量生产,以及使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所有这一切表明,同“无计划的资本主义”相比,政府能够更有效地管理经济。战后通过的主要法令之一是1946年的“就业法”。该法令表达了政府在维特“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方面的责任。这实际上是把凯恩斯的政策变成了法律。
战争对公众态度的影响与萧条所产生的影响极为相同。萧条使人们相信资本主义有毛病;战争使人们相信中央集权的政府是有效的。其实,两种结论都不正确。萧条是由于政府的无能造成的,而不是由于私人企业。在战争中,为了一个压倒一切的目的,政府可以暂时行使巨大的控制权。这个目的是几乎全体公民所共有的,他们都乐于为它作出重大牺牲。而政府为促进含糊不清的所谓“公共利益”永久控制经济,则是另一回事。这个“公共利益”是由公民们的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愿望构成的。
战争结束时,中央规划经济似乎成了未来的潮流。其结果受到一些人的衷心欢迎,他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新世界的黎明,大家将平等地分享富裕生活。其他人,包括我们在内,则是同样衷心地感到恐惧。在我们看来,它是走向专制和苦难的转折点。迄今为止,无论是前者的希望还是后者的恐惧,都没有成为现实。
政府的作用扩大得多了。然而,这种扩大并没有采取我们许多人曾经担心的那种形式,即中央制定具体经济计划,并对工业、金融和商业实行愈来愈广泛的国有化。人们根据以往的经验不再制定具体的经济计划了,部分地是由于它未能成功地实现已宣布的目标,同时也是由于它与自由的原则相冲突。这种冲突明显地表现在英国政府企图支配人民就业上。公众的反抗迫使政府放弃了这种企图。英国、瑞典、法国和美国的国有化工业效率极其低下,亏损额极其巨大,以致今天只有少数顽固不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认为进一步国有化是可取的。一度曾广泛为人接受的,以为国有化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幻想破灭了。诚然,现在政府有时仍然对个别部门和企业实行国有化,如美国的铁路客运和部分货运、英国的雪兰汽车公司以及瑞典的钢铁业。但实行国有化的原因却大不相同:有的是由于市场情况要求削减服务,但消费者希望予以保留,由政府补贴;有的是由于无利可图的企业的工人害怕失业。甚至那些支持这种国有化的人们,也不过是将它看成是不得已的事情。
计划和国有化的失败,并没有解除要求建立更为庞大的政府的压力,只是改变了压力的方向。政府的扩张现在采取了实行福利计划和开展调节活动的形式。正如W·艾伦·沃利斯用另一种说法所阐述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关于生产手段社会化的论据一个又一个地被戳穿,在理论上破产了,现在又谋求生产结果的社会化。”
在福利方面,方向的改变导致了最近数十年福利事业的激增,特别是在1964年林顿·约翰逊总统宣布“向贫穷开战”之后。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和直接救济等“新政”时期实行的计划,扩及到了新的集团;付款额增加了;增添了医疗照顾、医疗补助、食品券和其他许多计划。公共住房和城市复兴计划也扩充了。现在总共有数以百计的政府福利和收入转让计划。1953年,为把零散的福利计划集中起来,建立了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开始时预算为二十亿美元,不到国防开支的5%。而二十五年后的1978年,它的预算达到一千六百亿美元,为陆海空三军总开支的一倍半。它的预算之大在世界上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政府的预算和苏联政府的预算。该部管辖着一个庞大的王国,渗透到全国的每个角落。国内每一百名雇员中就有一名以上受雇于这个卫生、教育和福利王国,不是直接为该部服务,就是为由该部负责的、但由州或地方政府机构执行的计划服务。我们大家都受到了其活动的影响。(1979年底,从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分离出了一个教育部。)
谁也解释不了下面这样两个表面上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是人们对福利事业激增的后果普遍不满;一是人们继续施加压力要求进一步扩大福利事业。
目标都是崇高的,结果却令人失望。社会保险开支剧增,政府在财政上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公共住房和城市复兴计划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提供给穷人的住房。尽管就业人数不断增加,但接受公共补助的名单却越来越长。普遍一致的看法是,福利计划一团糟”,充满弊端和腐化。全国大部分医药费用由政府支付后,病人和医生却都抱怨开支剧增,抱怨医疗越来越缺少人情味。在教育方面,随着联邦政府干预的扩大,学生的成绩不断下降(见第六章)。
这些好心的计划接连遭到失败,并非偶然,也不单单是因为实施方面的错误所造成。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用恶劣的手段来达到良好的目的。
尽管这些福利计划失败了,然而,要求扩大这些计划的压力却有增无减。有人把失败归咎于国会在拨款时太小气,因而呼吁实施更广泛的计划。某些计划的得益者为进一步扩大这些计划而施加压力,其中首先就是实施这些福利计划的大批官僚。
一个吸引人的代替当前福利制度的办法是,向收入低于法定标准的家庭提供联邦补助。这个主张得到了具有各种不同政治信仰的个人和集团的广泛支持。目前已有三位美国总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然而,这种建议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似乎难以在政治上付诸实施。
现代福利国家的出现
最早大规模采用福利措施(这些措施现在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普遍采用)的现代国家,是“铁面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统治下的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提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社会保险方案,向工人提供事故、疾病和老年保险。他的动机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出于对下层群众的家长式的关心,同时也是狡猾的政治手腕。他的措施是用来破坏当时刚刚出现的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吸引力的。
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那样的一个本质上是贵族独裁的国家(用今天的行话来说就是右派独裁国家),竟会带头采用通常只有社会主义和左派才会采用的措施,似乎是咄咄怪事。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即使撇开俾斯麦的政治动机,也是如此。专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徒们都信奉中央集权,信奉靠命令进行统治,而不靠自愿合作。他们的分歧在于由谁来统治:是由血统决定的杰出人物来统治,还是由择优而取的专家来统治。他们都非常真诚地宣称,他们想要提高“全体大众”的福利;宣称他们知道什么是“公共利益”,而且知道怎样才能比一般人更好地为其服务。为此,他们都宣扬家长式的哲学。但是,一旦掌权,他们就都会在“全体福利”的幌子下,为其本阶级谋利益。
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保险措施更为接近的先例是英国采用的措施。这些措施始于1908年通过的养老金法和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
养老金法规定给予任何年过七十、收入低于规定数额的老年人以周养老金,金额按领取者的收入情况而定。它绝非捐助性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直接救济,即在英国存在了数百年的济贫法的延续。然而,正如A.V.迪塞指出的,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养老金被认为是一种权利。用养老金法中的话来说,不能因为领取养老金而“剥夺人们的任何公民权、权利或特权,也不能因此而使人们丧失任何资格”。养老金法颁布五年后,迪塞在评论该法令时写道:“一个乐善好施的聪明人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领取养老金也即救济金的人依然有权参加下院议员的选举,这种规定是否将对整个英国有利。”当时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谁也不会感到奇怪,但现在如果接受政府的慷慨赐与意味着丧失选举资格,那就是打着灯笼也不会找到一个有选举资格的人。这说明我们在福利国家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多么远。
国民保险法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第一,给所有受雇于联合王国的年龄在十六至七十岁之间的人保健康险,即保证他们有钱看病;第二,给受雇于该法令规定的那些部门的人保失业险,即保证他们在失业期间得到补助。”与养老金不同的是,国民保险法是捐助性质的,它的资金由雇员、雇主和政府共同负担。
由于它是捐助性质的,也由于它着眼于防止意外事故,该法令甚至比养老金法还要激进,更离开了以前的做法。迪塞写道:
根据国民保险法,国家招致了新的、可能是很沉重的负担。而挣工资的人则得到了新的、很广泛的收益。……在1908年以前,一个人不论贫富,是否为自己的健康保险,完全是每个人自由定夺的问题。他的选择同他要穿一件黑色上衣还是一件褐色上衣一样,与国家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国民保险法到头来会给国家,也就是给纳税人带来比英国选民们所预料的要沉重得多的责任。……失业保险……实际上是国家承认自己有责任使每一个人免受失业之苦……国民保险法正符合社会主义的理论。它与自由主义,甚至与1865年的激进主义很不协调。
美国早期的这些措施,同俾斯麦的措施一样,表明了贵族统治与社会主义的相近之处。1904年,温斯顿·丘吉尔脱离贵族的保守党,加入了自由党。他作为劳合·乔治内阁的成员,在制定社会改革的法令方面起了主导作用。改换政党(后来证明只是暂时的)并不象半个世纪以前那样,需要改变原则,半个世纪前,自由党对外实行自由贸易,对内实行自由放任主义。他所提出的社会立法,虽然在范围和种类上同以前的立法有所不同,但还是继承了家长式工厂法的传统。该法令是十九世纪主要在所谓的激进保守党人的影响下通过的。这批激进保守党人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贵族,浸透着要靠工人的赞同和支持,而不靠强制来照顾工人阶级利益的责任感。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英国成为今天的样子更多地要归功于十九世纪保守党的原则,而不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思想。
无疑,影响罗斯福“新政”的另一样板是瑞典。瑞典走的是“中间道路”,这是马奎斯·蔡尔德1936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瑞典于1915年颁布了强制性的养老金法,该制度的资金来自人们的捐助。规定给予所有年过六十七岁的人以养老金,不论其经济状况如何。养老金的数目依个人向该制度捐款多少而定。该制度也得到政府的财政补助。
除养老金和后来的失业保险外,瑞典还大规模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兴建公共住房以及建立消费者合作社。
福利国家的结局
长期以来被标榜为福利国家的成功典型的英国和瑞典,遇到了愈来愈多的困难,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英国感到越来越难以承担日益增加的财政负担。税收成了不满情绪的主要根源。通货膨胀更给人们的不满情绪火上加油(见第九章)。一度成为福利国家桂冠上的明珠而且至今仍被多数英国公众视为工党政府的伟绩之一的国民保健事业,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境,受到罢工、费用上涨和病人等候时间延长等问题的困扰。越来越多的人转而依靠私人开业医生、私人健康保险、私人医院和私人疗养所。尽管私人成份在整个健康事业中仍占很小部分,但这部分却正在迅速增长。
英国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一起增长。政府不得不收回它实现充分就业的许愿。最糟糕的是,英国的生产率和实际收入再好也只能算是停滞不前,这使它大大落后于欧洲大陆上的邻邦。保守党在1979年选举中大获全胜是这种不满情绪的集中体现。这一胜利是由于玛格丽特·撒切尔保证彻底改变政府的政策而获得的。
瑞典的情况比英国好得多。它在两次大战中都没有负担,从中立地位中的确得到了好处。尽管如此,它近来也经历了与英国同样的困难: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高额所得税使一些最有才能的人移居国外;人们对社会纲领普遍不满。在这里,选民也以投票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意见。1976年,选民们结束了社会民主党四十多年的统治,代之以其他政党的联合执政。然而,政府的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在美国,纽约市是企图依靠政府规划来做好事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纽约是美国最注重福利的城市。按人口计算,纽约市政府的开支比美国其他任何城市都大,为芝加哥的两倍。我们可以从纽约市长罗伯特·瓦格纳1965年的预算演说中看到指导该市活动的基本原则,他说:“我不主张让财政问题来限制我们应对满足市民的基本需要承担的义务。”瓦格纳及其继任者对市民的“基本需要”作了非常广义的解释。但是,更多的金钱、更多的福利计划、更多的税收都无济干事。它们导致了财政上的灾难,不要说瓦格纳讲的广泛需要,就连起码的“人民的基本需要”也未能满足,只是靠了联邦政府和纽约州的资助才免于破产。这种资助的代价是纽约市交出了控制自己事物的权力,受到了州和联邦政府的严密监护。
纽约市民自然要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归咎于外界势力的影响。但是,正如肯·奥雷塔在新近的一本书中写道的,纽约“并非出于被迫,搞那规模巨大的医院和市立大学体系,也没有谁迫使它实行免费教育,无限制地招生,忽视预算的限制,征收国内最高的赋税,胡乱借款,向中等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严格控制房租,给城市工人以优厚的养老金、工资和其他小恩小惠。”
他讽刺道,“受自由主义的热忱和财富再分配的理想主义信念的驱使,纽约的官员们帮助把许多税款和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分配给了纽约以外的地方。”
值得庆幸的是,纽约市不具有发行钞票的权力。它不能利用通货膨胀作为征税的手段,这才延迟了灾祸的到来。可惜,它并不正视自己的问题,只是向纽约州和联邦政府求救。
让我们更加仔细地看看以下几个例子。
社会保险
美国在联邦一级的主要福利国家项目是社会保险。它包括对老年、遗属、残废和健康的保险。正如巴里·戈德华特在1964年发现的,一方面,它是一头任何政治家都不敢碰的圣牛;另一方面,它又是众矢之的。领取津贴的人抱怨说靠补助金维持不了应有的生活水平。为社会保险纳税的人们则抱怨负担太重。雇主们抱怨说,在雇主多雇一名工人所花的钱和这个就业工人所得的净收入之间插进这些税造成了失业。纳税人抱怨说,这个未备基金的社会保险系统的负担总额已达数百亿美元,即便是目前的高税率也不能维持很久。这一切抱怨都有其道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实行社会保险和失业保险,是为了使工人能够为自已准备退休金或暂时失业时的补贴,而不必依靠救济。政府只是补贴那些真正贫穷的人,而且本来打算随着就业情况的好转和社会保险事业的普遍开展,逐步取消政府救济。这两个计划开始时规模都很小,但后来却盲目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目前看不出社会保险有取代政府救济的迹象。在耗资和领取补助的人数方面,二者都空前巨大。1978年为退休、残废、失业、医疗保健和遗属抚恤支付的社会保险金总共超过一千三百亿美元,领取者超过四千万。四百多亿美元的政府救济发给了一千七百多万人。
为把讨论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这一节的探讨将仅限于社会保险的主要部分,即对老年人和遗属的补贴上。他们得到的津贴几乎占整个福利开支的三分之二,人数占领取福利金总人数的四分之三。下一节再讨论政府救济计划。
社会保险法于本世纪三十年代通过,自那时以来,社会保险事业便贴着假标签,通过骗人的广告宣传,被到处推销。如果是一家私营企业进行这种骗人的宣传活动,无疑会遭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斥责。
一直到1977年,在一本题为《大众社会保险》的未署名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发行了上百万份的小册子上,年复一年刊载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社会保险的基本思想很简单:就是在就业期间,雇主、雇员和自雇人员支付社会保险金,用这些钱设立特殊的信托基金。当工人由于退休、残废或死亡而没有收入或减少了收入时,将按月给予一定的、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家庭收入的减少。”
以下是奥韦尔(译注:奥韦尔是美国社会党人布莱尔的笔名,下文《一九八四年》一书的作者。)的矛盾观念。
工资税被称为“捐款”(或象该党在《一九八四年》那本书中说的,“强制即自愿”)。
在人们的想象中,信托基金似乎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它们的数目向来很少(1978年6月,老年和遗属保险基金为三百二十亿美元,按当时的支出情况,不足半年之用),而且,只是政府的一个机构答应向另一机构付款。当前按社会保险法已经答应给退休或尚未退休的人的养老金的总值,已达数万亿美元。要证明小册子的话正确,就需要这样数目的信托基金(用奥韦尔的话说,“少即多”)。
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工人的“福利”是靠自己的“捐款”来支付的。实际上,支付给退休工人、退休工人家属和工人遗属的福利金,是从就业工人那里征收的税款。根本就没有设立真正的信托基金(“我即你”)。
今天纳税的工人从信托基金那里得不到保证,他们退休时将得到福利。任何保证都取决于未来的纳税人,要看他们是否愿意为现在的纳税人许诺给自己的津贴纳税。这种单方面的“隔代契约”被强加给一代代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同意。这与“信托基金”是两码事,倒不如说更象一封连锁信。
现在发行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小册子还说:“在美国,每十名就业者中有九名为自己和家庭挣得社会保险计划的保障。”
更为矛盾的是:现在每十名就业者中,有九名在为非就业者的津贴纳税。向私人养老金机构捐款的人可以说是在为自己“挣取”保障。而向政府机构纳税的人则不能说是在为自己和家庭“挣取”保障。他只是在政治意义上“挣取”保障,即满足政府的一定要求以取得享受福利的资格。现在接受补助的人们所得到的,要比他们自己缴纳的税和别人为他们缴纳的税的总值高得多。而许诺给现在缴纳社会保险税的年青人的,要比他们将要缴纳的税和别人将为他们缴纳的税的总额少得多。
社会保险并不是一种交多少钱就能拿到多少津贴的保险计划。甚至它的最坚决的支持者也承认,“个人所捐的钱(即工资税)与他所得到的津贴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社会保险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税和一种特殊的转移开支计划的混合体。
有意思的是,我们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个人,不论其政治倾向如何,会替税收制度或福利制度本身辩护。如果把这两种制度分开来考虑,哪种制度也不会被人们采纳。
至于福利方面的赋税,虽然最近作了一些小改小革(即根据收入情况给予回扣),但仍然是对所有等级的工资按统一比率征税。因而这是一种累退税,低收入者负担最重,是对工作征收的税,使雇主不想雇用工人,人们不想找工作。
至于津贴的安排,它既不由领取者所付的钱数来决定,也不由他的收入情况来决定,既不能公平地偿还原先所付的钱,也不能有效地帮助贫困者。在所付的税款和所得到的津贴之间虽然也有某种联系,然而它最多不过是一块遮羞布,以使人们能大言不惭地把这种结合叫做“保险”。一个人能够得到多少津贴完全取决于各种偶然因素。如果他恰好在保了险的行业工作,他可得到津贴;如果他恰好在一个没有保险的行业工作,他就得不到津贴。如果他在一个保了险的行业中干的时间不长,不管他多么贫困,也是什么也得不到。而一位从不工作的妇女,如果她是一位可以享受最高津贴的人的妻子或未亡人的话,那她得到的津贴会和一位同她情况相同的劳动妇女除工资外得到的津贴相等。一位年过六十五岁的人,如果决定去干活,而且每年挣得中等以上的收入,那他不仅得不到津贴,更倒霉的是,还要额外纳税——想来是为了补偿那没有支付的津贴。这种事例举不胜举。
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保险计划是“新政”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该计划把一种人们不能接受的赋税和一种人们不能接受的补贴方法结合在一起。我们很难想象有哪个异想天开的计划能比这个计划取得更大的成功。
纵观社会保险方面的各种文章和书籍,我们对那些用来为该计划辩护的论证感到震惊。一些不会对自己的孩子、朋友或同事撒谎的人,一些在日常的私人交往中最让人信得过的人,竟然会在社会保险这一问题上宣传错误的观点。他们的才智和对相反观点的揭露,使人难以相信他们在进行这种宣传时,是出于无意和无知。他们显然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精华,最知道什么对别人有益,认为有责任和义务去说服选民为那些会对他们有益的法律投票,为此,即使欺骗他们也在所不惜。
长期以来,社会保险计划的财政困难是由一个简单的事实造成的: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数,比可以为福利津贴纳税的人数增长得快,而且今后还将更快。1950年,每一个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有十七个人为其纳税;到1970年只剩下了三人为其纳税;如果目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到二十一世纪初,最多将只有两人为其纳税。
上述情况表明,社会保险计划把收入从青年人那里转移给了老年人。从整个历史来看,这种转移在某种程度上早已存在了,以往青年人总是供养他们的父母或其他上了年纪的亲属。的确,在许多象印度那样有着很高死婴率的贫穷国家。养儿防老是造成高出生率和大家庭的主要原因。社会保险和早先供养父母的习惯的区别在于,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非个人的事情,而供养父母则是自己愿意的个人私事。道义的责任是个人而不是社会的事情。孩子照顾自己的父母是出于爱或责任感。现在,他们为供养别人的父母解囊是由于受到政府的强制和出于恐惧。早先的那种转移加强家庭的纽带,而强制的转移则削弱这种纽带。
【按:美国以前也是祖孙三代同堂的社会,直到社会保障制度的扩大。】
除了从青年人向老年人的这种转移,社会保险还包括从不那么富裕者向比较富裕者的转移。福利津贴的发放确实是偏于照顾工资较低的人。然而,这种照顾被另外一种情况大大地抵消了。穷人家的子弟开始工作因而开始纳税的年龄都比较早;而富人家的子弟则晚得多。另一方面,就生命周期而言,低收入者的寿命平均比高收入者的寿命短。结果,穷人纳税的年头比富人长,领取福利津贴的年头比富人短,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穷人。
社会保险的其他一些特征更加强了这种反常的效果。福利津贴领取者的其他收入越高,从所得税中扣除的福利额就越大。对于年龄在六十五至七十二岁(1982年将改为七十岁)之间的老人,发给的津贴数额完全取决于他在那些年的工资收入,而不看其他方面的收入——有一百万美元的股息收入也不妨碍领取社会保险津贴;而年薪超过四千五百美元的人,却要为他所得的每两美元收入损失一美元的津贴。
总而言之,社会保险是“董事法规”在起作用的极好范例,即“公共开支是为了中等阶级的基本福利,而作为公共开支来源的赋税则主要由穷人和富人来负担。”
政府补助
讨论“一团糟的福利”可以比讨论社会保险简单得多,因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看法比较一致。我们现行的福利制度的弊病已被广泛地认识到了。尽管富裕程度在增长,但领取救济金的人数也在增加。庞大的官僚机构主要忙于来往公文的处理,而不是真正为人民干事。人们一旦靠上救济,就很难脱离救济金而生活。国家日益分化为两类公民,一类人领取救济,另一类人为救济出钱。那些领取救济的人就不想再挣钱了。救济金在国内各个不同的地方差异很大,这鼓励了人们从南方和农村地区向北方特别是城市中心移居。尽管经济情况可能相同,但是,正在接受救济或受到过救济的人与没有受过救济的人(即所谓穷工人)却往往受到政府的不同对待。贪污腐化和欺诈行贿,以及大事报导的福利“皇后”驾着用多种救济券买来的高级轿车到处周游的新闻,一次又一次地激起公众的愤怒。
【按:对比国内的红十字会,美国情况还算好点的。】
在对福利计划的抱怨增加的同时,受埋怨的福利计划的数目却在不断增加。已经通过的帮助穷人的联邦计划,乌七八糟地有一百多个。其中主要的计划有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对老年人的医疗照顾、对穷人的医疗补助、对有子女家庭的补助、保险收入补助、食品券;还有大多数人未听说过的无数小计划,如对古巴难民的援助、对妇女、婴儿和儿童的营养补助、对婴儿的特别照顾方案、房租补助、城市灭鼠方案、综合治疗血友病中心等等。许多计划是重叠的,有些设法得到多项福利补助的家庭,其最后的收入肯定要比全国平均收入还高。而另一些家庭或则由于行动得慢了些,或则由于不太关心这种事,往往申请不到补助来减轻他们真正的贫困。然而,每项计划都需要有官僚机构去管理。
社会保险每年耗资一千三百多亿美元,除此之外每年还要在这些福利计划上开支大约九百亿美元(十倍于1960年的开支)。这显然是太多了。1978年的所谓贫困线是:一个非农业的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在七千美元以下。据人口普查估计,当时大约有两千五百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中。这是个粗略的过高的估计,因为它仅仅根据工资收入来划线,全然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收入,如房产、花园、食品券、医疗补助、公共住房。有些研究报告认为,算上这些收入的话,“人口普查”的数字可以减少一半或四分之三。但是,即使根据人口普查的估计数字来计算,福利计划的开支分给每个贫困线以下的人,也合三千五百美元左右,分给每个四口之家合一万四千美元左右。约为贫困线水平的两倍。如果这些福利资金确实都花在“穷人”身上,就不会还有穷人,至少他们也可以舒服地过富裕的生活了。
显然,大部分福利开支没有用在穷人身上。其中有些被行政开支挪用,以优厚的薪金维持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有些到了那些绝不能被认为是穷人的手中。这些人中间有领取食品券或其他补助的大学生,有收入相当不错而又领取住房补贴和其他各种我们想象不到的补贴的家庭。还有些则到了骗取福利金的人手中。
我们有必要在这些福利计划上多费些口舌。同领取社会保险津贴的人们不同,靠这一巨额福利款项补助的人们的平均收入,可能比为补助他们而纳税的人们的低,不过即使这一点也很难确定。正如马丁·安德森所说:
“我们的福利计划可能效率很低,弊病很多,管理质量很差。有些计划彼此重叠,福利金的分配很不公平,而且没有能够在物质上刺激人们去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倒退一步,按照以下两个基本标准来考查各色各样的福利计划,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两个标准是:福利计划服务的对象之广泛和人们得到的服务之全面。按这两个标准衡量,我们的福利制度是辉煌的成就。”
住房补助
政府提供住房的计划在“新政”年代初始之时规模不大,后来迅速扩大。1965年新设立了一个部,即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该部现有近两万名雇员,每年开支一百亿美元以上。联邦住房计划得到各州和市政府计划的补充,特别是在纽约州和纽约市得到了大力补充。开始实行该计划时,政府只是为低收入家庭建造住房。战后,又增添了城市复兴计划。许多地区扩大了住房计划,向“中等收入的”家庭也提供公共住房。最近,又增加了“房租补贴”计划,政府为租赁私人住房提供房租补贴。
按最初的目标来看,这些计划显然是失败了。遭到破坏的住房,比建造起来的住房要多。住在享有房租补贴的公寓里的家庭,得到了好处。而那些由于自己的住房毁坏,无处栖身而被迫迁入更差的住宅的人家,住房情况则有所恶化。今天美国的住房和分配情况胜于公共住房计划开始实行之日,然而,这全赖私人企业之力,跟政府补贴没有多大关系。
公共住房常常沦为贫民窟和犯罪特别是青少年犯罪的温床。最明显的例子是圣路易斯的普鲁特·艾戈公共住房工程。该工程是一个占地五十三英亩的巨大的公寓群。其设计曾荣获建筑奖。然而,它已损坏得如此严重,以至不得不炸掉它的一部分。那时节,它的两千个单元中只有六百个住了人。人们说,它看上去象是个发生过巷战的地方。
1968年游历洛杉矶市瓦茨区时遇到的一件事,我们至今记忆犹新。陪同我们参观的是一位管理完善的自助工程的负责人。该工程是由工会倡议的。当我们赞扬这一地区的一些公寓时,他气愤地打断了我们的话,说:“瓦茨区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正是那些公共住宅。”他接着又说:“你怎么能指望那些住在完全由破裂家庭组成的开发区里、几乎完全靠福利救济为生的年轻人,养成良好的品德呢?”他还慨叹开发区对少年犯罪和附近学校产生的不良影响。那些学校的孩子很多都来自破裂的家庭。 最近,我们从纽约南布朗克斯的一个叫做“血汗资本”住房工程的领导人那里听到了类似的议论。该地区看上去象是被轰炸过的城市。许多建筑由于房租控制而被抛弃,另一些则毁于暴乱。“血汗资本”团体同政府商定,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复那些被废弃的住房,修好后,所有权归私人所有。开始时,他们从外界只得到少数私人捐款的支援,最近,也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些帮助。
当我们问他人们为什么不直接搬进公共住宅而费这么大的力气去修复旧房时,他作了我们在洛杉矶听到的同样的回答,不过又添了一句说,建造并拥有自己的住宅会使参加这一工程的人具有一种自豪感,这会使他们精心维修住宅。
“血汗资本”团体得到的政府援助,一部分是工人的劳务。这些工人根据综合就业训练法由政府支付工资,被派到各种不同的公共工程去接受训练,以便获得技能后能在私人企业中就业。当我们问他,“血汗资本”团体是愿意让综合就业训练法雇用的工人来帮忙,还是宁愿得到支付给工人的钱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宁愿得到钱。总之,人们在这种自助工程上表现的自力更生精神和干劲与他们在公共住宅工程上表现的那种明显的冷漠、无谓和厌倦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看到这些是令人鼓舞的。
纽约市实施的据说可以防止“中等收入家庭”逃离城市的住房补贴计划,情景大不一样。宽敞豪华的公寓以补贴的方式租给那些只有在极宽裕的意义上才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的家庭。对每套公寓的补贴平均每月在二百美元以上。“董事法规”又在起作用。
城市复兴计划旨在消灭贫民窟——“城市枯萎病”。对于需要重建的地段,政府出钱征用和清除,清理了的地皮大多以人为的低价供私人开发者利用。城市复兴计划“要拆迁四座住宅,才能建造一座住宅,拆迁的大都是黑人居住的房屋,而建造好的房屋大都供中等或上等收入的白人家庭居住。”原先的住户被迫迁移到其他地方,常常又使新的地段害“枯萎病”。某些批评者把城市复兴计划称为“贫民窟迁移计划”和“黑人迁移计划”,倒是名副其实的。
公共住宅和城市复兴计划的主要受益者并不是穷人,而是某些房地产主(他们的财产被政府征购来建造公共住房或者其财产正好位于要重建的地段)、中等和上等收入的家庭(它们能在高价公寓中或者在那些常是靠拆除低租房子重新盖起的市内公寓中找到住房)、市区商业中心的开发者和占有者以及能够利用城市复兴计划改善自己附近环境的大学和教会等公共机构。
正如《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篇社论指出的那样:
“联邦贸易委员会考察了政府的住宅政策,发现这些政策并非完全出于利他主义的目的。该委员会的一份政策简报发现,联邦住房政策的主要推动者似乎是那些靠盖房发财的人,如承包商、银行家、工会、建筑材料商等。一旦住宅建成后,政府和上述各色各样的‘赞助人’就对它不那么感兴趣了。因此,联邦贸易委员会常常听到人们抱怨住宅的质量,指责根据联邦计划建造的房子屋顶漏水,管道不足和地基不牢等等。”
另外,由于政府实行房租管制等措施,即使不是由于故意毁坏,一些低价出租的住宅也因无人修缮而日益破旧。
医疗照顾
医药是政府在最近一个时期扩大其作用的一块福利阵地。在公共卫生(环境卫生、传染 病等)以及提供医院设施方面,州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发挥作用,联邦政府也在较小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另外,联邦政府还为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提供医疗照顾。但直至1960年,政府用在人民保健事业方面(即不包括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的开支仍然不到五十亿美元,只占国民收入的1%强。自1965年实施医疗照顾方案和医疗补助方案后,政府在保健事业方面的开支迅速增加,1977年达到六百八十亿美元,约占国民收入的4.5%。政府在全国医疗总开支中所占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从1960年的25%增加到1977年的42%。然而,要求政府起更大作用的呼声仍然越来越大。卡特总统已对实施国民健康保险计划表示赞同,但限于财力,只能以有限的方式来搞。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没有这种顾虑,他主张立即通过法律由政府对全国公民的保健负完全责任。政府在医疗上的额外开支与私人健康保险的开支齐头并进。从1965年到1977年,医疗费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长了一倍。医疗设施也增加了,但费用没有增加得那么快。其必然结果是医药费和医生以及其它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员的收入猛增。
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曾试图管理医疗服务并压低医生和医院的收费。这是它应当做的事。政府既然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自当关心花了钱得到了多少好处:这叫作出资者做主。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其最终结果不可避免地会是医疗社会化。
【按:这里的医疗社会化其实是政府所有化,和国内说法不同。】
国民健康保险是使人产生误解的另一个例子。国民健康保险不同于私人保险:在你所交的钱与你可能得到的福利总额之间没有联系。另外,国民健康保险并不是为了给“国民的健康”(一个毫无意义的词)保险,而是为本国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它的倡议者所提倡的实际上是社会化的医疗制度。著名的瑞典医学教授、瑞典一家大医院的内科主任根纳·俾奥克博士曾写道:
“几千年来的行医过程是病人作为医生的顾客和雇主。今天,国家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自命为雇主,要由它来规定医生工作的框框。这些框框可能不会——最后一定不会——限于工作小时、薪金和药品的规格;它们可能影响病人和医生的所有关系。……如果今天不打这一仗并取得胜利,明天就没有仗可打了。”
美国提倡医疗社会化的人们,为了使其事业名正言顺,过去总是引用英国,最近总是引用加拿大的例子作为成功的样板。加拿大最近才实行医疗社会化,还不能对它下结论,因为新扫帚总是扫得特别干净,但它现在已经出现了困难。美国的国家卫生局已经建立了三十多年,对其作用我们现在完全可以下一结论了。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被举出来代替英国作为样板的原因。英国医生马克斯·甘蒙博士用了五年时间研究国家卫生局。他在1976年12月提出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国家卫生局)实际上使全国所有医疗服务都由中央政府提供资金,由中央政府进行控制。在过去二百年中发展起来的民间医疗事业几乎已完全被消灭。现行的强制性医疗制度经过改组实际上已成为普遍的医疗制度。”
另外,“在国家卫生局建立的最初十三年中,实际上没有新建一座医院,而现在,1976年,英国拥有的医院床位比在1948年7月刚建立国家卫生局时还要少。”而且,这些床位中的三分之二是设置在1900年以前由私人医生和私人资金建立起来的医院里的。
甘蒙博士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他所谓的官僚取代论:即机构越官僚化,无用工作取代有用工作的程度也越大,这可以说是帕金森定理的一种有趣的延伸。他用英国1965至1973年医院服务的材料证明了这一理论。在这八年期间,医院的工作人员总数增加了28%,行政和协助办事人员增加了51%,但按每日床位的平均使用率来计算的产量却下降了11%。而且正如甘蒙博士赶忙补充的,这并非是由于缺少病人使用的床位。在任何时候,都总有六十万左右的人等待医院的床位。许多被保健机构认为是可收可不收或可以等些时候的病人,要等几年才能得到手术治疗。
【按:英剧《是大臣》第二季第一集中的圣爱德华医院勉强算只有一名病人,却有五百名办事人员。编剧对社会的很多方面了解很是深刻。】
医生纷纷逃离英国。每年移居国外的医生约相当于英国医学院校毕业生人数的三分之一。近来,私人行医、私人健康保险、私人医院和私人疗养所迅速增加,也是对国家保健事业不满的结果。
在美国,实行医疗社会化的论据主要有两个:一,大多数美国人负担不起医药费;二,医疗社会化将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医药费用。第二个论据可以立即排除;至少是在有人能找到一个政府管理比私人经营更为经济的事例以前。至于第一个论据,可以说人民总是要这样或那样支付医药费用的,问题只在于,是人民直接自行支付这些钱,还是通过政府官僚来支付。这些官僚们会从中抽去相当大的一部分作为他们自己的薪金和开支。
无论如何,大多数美国家庭支付得起普通医药费用。他们可以进行私人保险,以应付意外的特大开支。住院费用的90%已经由第三者偿付。人们有时肯定会遇到特殊困难,这时应该由私人或政府提供某种帮助。但偶尔帮助人们克服困难,并不能证明强加给全国人民一套制度是合理的。
我们可以从以下的比较感觉到医疗费用的巨大:私人和政府花在医疗事业上的费用,总共为住房建设费用的三分之二,汽车制造业开支的四分之三,烟酒制造业开支的两倍半。烟酒业的开支无疑增加了医疗费用。
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实行医疗社会化。相反,政府在医疗方面的作用已经太大了。它的作用的任何进一步扩大将违反病人、医生和保健人员的利益。在第八章“谁保护工人”中,我们将讨论医疗的另一方面,即发放医生执照和这一措施对美国医学会的权力的影响。
福利国家的谬论
为什么这些计划都如此令人失望呢,它们的目标肯定是人道的和崇高的。但为什么没有成功呢。
新纪元初始之时,一切看来都好。要救济的人很少。能资助他们的纳税人很多——这样每人只需支付不大的数目,就可以为少数穷人提供可观的救济金。随着福利计划的扩大,这些数字发生了变化。今天,我们大家都从一个口袋里掏出钱,又把它(或它可以买得的东西)装进另一只口袋里。 把开支作一简单的分类,就能够说明为什么这一过程会导致不良的结果。当你花钱时,可能花的是你自己的钱,也可能是别人的钱,你可能是为自己花,也可能是为别人花。把这两对可能性编在一起,可以得出以下简图中归纳的四种可能性:
你是花钱者
| 谁的钱\为谁花 | 你 | 别人 |
|---|---|---|
| 你的 | I | II |
| 别人的 | III | IV |
Ⅰ类指的是你为自己花自己的钱,如你到超级市场买东西。你显然有强烈的愿望,既要省钱,又要使所花的每一美元都花得尽可能合算。
Ⅱ类指的是你为别人花你的钱,如你买耶诞节或生日礼物。你会象Ⅰ类中那样希望省钱,但并不同样想要花得最上算,至少根据接受人的爱好来判断是如此。当然,你要买接受者喜爱的东西,只要它能产生好的印象而又不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假如你的主要目的是让接受者能获得尽量多的价值,你会送给他现金,将Ⅱ类中由你花钱变为Ⅰ类中由他花钱)。
Ⅲ类指的是你为你自己花别人的钱。例如,可报销的用餐。你没有强烈的愿望要少花些钱。但你会有强烈的愿望想使钱花得上算。
Ⅳ类指的是你为另一个人花别人的钱。例如,你用报销单替另一个人付饭费。在这种情况下,你既不会想省钱,也不会想让客人吃得最为满意。然而,如果你同他一起用餐的话,那么,这顿饭就成了Ⅲ类和Ⅳ类的混合体,你就会有强烈的愿望满足你自己的口味,必要时可以牺牲他的口味。
所有福利计划不是属于Ⅲ类——如社会保险,福利金领取者可以按自己的愿望随便花他领到的钱——就是属于Ⅳ类——如公共住房;只是在Ⅳ类中带有一点Ⅲ类的特征,即管理福利计划的官僚们分享这顿午餐;而在Ⅲ类的所有计划中都有官僚们夹在福利金领取者中间。
我们认为,福利开支的这些特点是其缺点的主要根源。
立法者投票表决时是决定如何花别人的钱。选出立法者的选民在某种意义上是投票决定这是一个很好的表述方式,是我们和电视节目的到制片人埃本·威尔逊共同讨论产生的。
【按:政策可以设定为谁支持谁出钱。】
如何为自己花自己的钱,但不是在Ⅰ类那种直接花费的意义上。在个人缴纳的税款与他投票赞成的花费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实际上,选民同立法者一样,倾向于认为是别人在支付由立法者直接投票赞成、由选民间接投票赞成的计划。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僚们也花别人的钱。因此,开支数目激增也就不足为奇了。
官僚们为别人的需要花别人的钱。只有用良心,而不是用那强烈得多和可靠得多的私利的刺激,来保证他们以最有利于福利金领取者的方式花钱。这就造成花钱上的浪费和不求效果。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拿别人钱的引诱力是强烈的。包括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僚们在内,许多人都设法为自己得到钱,而不让钱落到别人手里。进行贪污和欺诈的诱惑力也是强烈的,而且并不总是能遭到反抗或制止。那些不愿进行欺骗的人,会用合法的手段使钱归于自己。他们会运动议员通过于他们有利的立法,定出他们能从中获利的规章。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员们会力求为他们自己得到更高的薪水和额外的好处——这正是较大的福利计划可以帮助达到的目标。
人们试图把政府开支归入自己的腰包,产生了两个不大容易被人查觉的后果。首先,它说明了为什么如此多的计划施惠于中等和上等收入者,而不是那些本应当得到好处的穷人。穷人变得不仅缺少市场上所看重的本事,而且缺少在政治斗争中成功地争得资金的本事。的确,他们在政治市场上的劣势看来比在经济市场上的劣势更大。一旦好心的改革者帮助通过了一项福利措施,转入下一项改革时,穷人就只好自己照料自己,他们几乎总是被那些已经表明更善于见机行事的集团所压倒。
第二个后果是,福利金领取者得到的净额,往往少于转移金的总额。如果有别人的一百美元可以攫取,那么为得到它你花上自己的一百美元也值得。花钱运动立法者和制定规章的当局,为政治运动和无数其他事项捐款纯属浪费——既损害出钱的纳税者,又无益于任何人。必须把它们从转移总额中除去,才得到净所得——当然,它们常常超过转移总额,结果剩下的不是净所得,而是净损失。
争取补贴的这种结果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有人要施加压力来增加开支和福利计划。最初的措施未能达到提倡它们的好心的改革者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就得出结论认为做得还不够。并谋求增添福利计划。他们同那些希望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僚们,以及相信能从福利开支中捞到油水的人们结成了同盟。
Ⅳ类开支还容易腐化接触到它们的人们。所有福利计划都使一些人处于决定什么对别人有利的地位。结果是,一部分人感到自己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另一些人则感到自己象孩子那样需要别人照顾。被救济者的独立自主的能力由于弃而不用而萎缩了。除了金钱的浪费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外,其最终结果是腐蚀了维持一个健全社会所必需的道德结构。
Ⅲ类或Ⅳ类开支的另一副产品具有同样的效果。除了人家白给你的钱外,如果你要花别人的钱,就只有象政府那样把别人的钱拿到自己手里。因此,福利国家到头来总是要使用强力,这一有害的方法往往使良好的愿望落空。这也是为什么福利国极其严重地威胁我们的自由的原因。
怎么办
大多数现行的福利计划,当初根本不应该制定。如果没有制定这些计划的话,许多现在依赖福利金的人很可能会成为自食其力的人,而不是受政府保护的人。这样做,对某些人来说一时可能显得不近人情,因为这使他们不得不干报酬低微而乏味的工作。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却是非常人道的。不过,福利计划既然已经实施,就不是一夜间能够一扫而光的了。我们需要某种方法使我们从目前所处的状况顺利地过渡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状况,为现在依赖福利金的人提供援助,同时鼓励人们从领福利金有条不紊地转到领工资。
这样一个过渡纲领可以增强个人责任感,结束目前把人们划分为两个阶段的状况,缩小政府开支和现在庞大的官僚机构,同时保障国内每个人的安全,到那时谁也不会再受贫困的煎熬。不幸的是,眼下要通过这样一个纲领似乎只是乌托邦的幻想。挡道的既得利益集团太多了,有思想上的、政治上的、财政上的,等等,许多许多。
尽管如此,看来仍值得向人们介绍这样一个纲领的主要内容。当然,我们并不指望它会在最近的将来被采纳,我们只想指明应该努力的方向,从而促进事态向这个方向发展。
这个纲领有两项基本内容:第一,改革现在的福利制度,用一个单一的内容广泛的现金收入补贴计划(这是一种与正所得税相联系的负所得税)取代目前杂七杂八的单项计划;第二,在履行现有义务的同时,逐步取消社会保险,要求人们自己为退休后的生活作出安排。
这种广泛的改革,将使我们目前实行的既不人道、又无效率的福利制度变为比较人道、比较有效的制度。它将向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确有保证的最低限度的补助,而不问他们需要的原因。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尽可能少的损害他们的名誉、独立性或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主动性。
一旦我们透过那掩盖正所得税的本质特征的烟幕,负所得税的基本概念就简单易懂了。根据现行的正所得税制度,允许你有一定数目不必纳税的收入。其确切数额,视你家庭人数的多少、你的年龄和你是否列举清楚你的扣除额而定。这个数额由以下几部分构成:个人豁免额、低收入免税额以及标准扣除额(最近它被重新定名为零级数额),总额相当于一般赋税优惠额。另外,据我们所知,还有偷税漏税的能手加进的许多数额,他们很会在缴纳个人所得税上玩一些鬼把戏。为便于讨论,让我们用“个人免税额”这个较为简明的英国术语来称呼这个基本数额吧。
如果你的收入超过免税额,超过的部分得按累进的税率纳税。如果你的收入低于免税额呢,在现行制度下,那免税额一般是无价值的。你只是无需纳税而已。
如果接连两年你每年的收入恰好与免税额相等,那么,在这任何一年中你都无需纳税。假设你这两年加起来的收入还是这么多,但有一半多是头一年得到,那你就有正数值的应纳税收入,也就是说你第一年的收入超过了免税额,因而必须纳税。而到第二年,你则有负数值的应纳税收入,也就是说免税额超过了收入。但一般来讲,你从免税额上得不到什么好处。最后这两年加在一起,你将比这笔收入均分在两年中缴纳更多的税款。
有了负所得税,你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未用上的免税额的一部分作为补贴。如果你得到的这一部分与正收入的税率相同,那么,无论你的收入在这两年中如何划分,你所缴纳的税款总额总是相等的。
当你的收入高于免税额时,你就要纳税,税额视收入额的多少而定。当你的收入低于免税额时,你会得到补贴,其数额根据未用上的免税额的多少而定。
正如我们所举的例子所表明的,负所得税将考虑到收入的波动,但这并不是它的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毋宁说是要提供一种简便的方法,确保每个家庭有一份最低的收入,同时避免庞大的官僚机构,使人们具有很强的个人责任感,打心里想去工作,想挣大钱来纳税而不是领补贴。
请看下面这个具体数字的例子。1978年,一个四口之家(其成员无人超过六十五岁)的免税额是七千二百美元。假定当时有所谓负所得税,其补贴率为未用上的免税额的 50% ,那么一个无收入的四口之家就有资格获得三千六百美元的补贴。如果这个家庭有人找到了工作,有了收入,补贴将被削减,但是,这个家庭得到的总收入(补贴加挣得的收入)将增加。如果收入为一千美元,补贴将减少到三千一百美元,而总收入上升为四千一百美元。实际上,所挣的收入一半用来弥补减少的补贴,一半用来增加总收入。一旦家庭所挣收入达到七千二百美元,补贴就降为零。七千二百美元是平衡点。在这个点上的家庭,既得不到补贴,也用不着纳税。如果家庭所挣收入继续增加,它就要开始纳税了。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研究行政管理的细节——补贴是按一星期,按两星期,还是按月支付,怎样检查执行情况,等等。所要说的只是:对这些问题都已作过彻底的研究,并拟有详细的计划,提交给了国会(这件事我们以后还要提到)。
负所得税制如能取代我们现有的许多专门的福利计划,我们现在的整个福利制度将会得到令人满意的改革。如果它只是变成整个福利垃圾堆里的又一件破烂,那就弊多利少了。
如果负所得税制果真取代了各种福利计划,那将带来巨大的好处。该制度是专门用来对付贫困问题的。它将以最实用的形式,即用现金来资助接受者。它是综合性的,而不是因为接受者年纪大,有疾残,患病,或生活在某一地区,也不是因为任何其他使人们在现行福利制度下可以得到救济金的原因。它给予资助,是因为接受者收入低。它明白地规定由纳税人承担费用。象任何其他设法减少贫困的措施一样,它也会减少促使人们自助的刺激。但是,只要把补贴率限定在合理的水平上,它就不会完全消除这种刺激。因为多挣一块美元,总是意味着有更多的钱可花。
同样重要的是,负所得税制可以免除目前管理这一大堆福利计划的庞大官僚机构。负所得税可以直接成为现行所得税制的一部分,并且可以一起管理。由于每个人都要填报所得税单,它可以减少现行所得税制度下的逃税漏税现象。可能要增添一些人员,但增添的人决不会多于目前管理福利计划的人。
通过取消庞大的官僚机构,使补贴制与税收制相互结合,负所得税可以铲除目前的不正常现象,即一些人——掌管福利计划的官僚们——操纵着他人的生计。它将有助于消除当前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级的状况:纳税阶级和依靠政府救济过活的阶级。只要平衡点和税率定得合理,负所得税制将比我们现行的制度省钱得多。
对于某些由于这样或那样原因无能力料理自己事务的家庭,给予个人帮助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由负所得税来维持穷人家庭的收入,这种帮助可以,而且会由私人慈善活动来提供。我们认为,现行福利制度最大的代价之一在于,它不仅破坏家庭,而且减少私人慈善活动。
社会保险怎么能够实现这一在政治上总是行不通的美妙梦想呢?
依我们看,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实行负所得税制与逐步减少社会保险结合起来,同时继续履行现有的义务。其方法如下:
1.立即废除工资税。
2.按现行法律规定的数额,继续付给现在享受社会保险的人以应得的钱。
3.给予每个已经挣得保险的工人以享受退休、残废或遗属福利津贴的权利。这些福利金是工人根据现行的法律迄今已付的税款和所挣得的收入使他有权获得的,但要减去由于废除工资税而今后少缴纳的税款所折合的福利金数额。工人可以选择他所要的福利津贴的形式,可以是将来的一份年金,也可以是公债,其价值与按照目前规定他有权得到的福利津贴的价值相等。
4.给予每个尚未挣得保险的工人一笔钱(同样采取公债券的形式),数目等于他或他的雇主为他已缴纳的税款的累计价值。
5.停止积累保险津贴,让个人按自己的愿望为退休后安排养老。
6.从总的税收和政府发行的公债中为上述第2、3、4项开支提供资金。
这样一个过渡性纲领丝毫不会增加美国政府的实际债务。相反,它会由于不再向未来的福利津贴接受者许诺而减少债务。它只是把现在隐蔽的债务公开化。它为现在未备基金的计划提供资金。这些步骤会导致大多数现存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立即解散。
逐步减少社会保险,将消除目前社会保险制度给就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意味着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它将增加个人储蓄,从而导致更高的资本形成率和更快的收入增长率。它将刺激私人养老金计划的发展和扩大,从而使许多工人感到生活更有保障。
哪些是政治上可行的?
这的确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不幸的是,在目前根本没有实施的可能。尼克松、福特和卡特这三任总统都考虑或推荐过包含有负所得税成分的计划。但政治上的压力迫使他们提出的计划只是作为现行福利计划的补充,而不是取代它们。补贴率都定得如此之高,以致这个计划对福利津贴领取者挣钱起不了什么刺激作用。这种畸形的计划只会把整个福利制度搞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尽管是我们最先提出用负所得税制代替目前的福利制度,但我却在国会作证,反对尼克松总统根据负所得税的想法提出来的“家庭补助计划”。
一项可实施的负所得税制,在政治上往往遇到两种互相关联的障碍。较为明显的障碍来自现行福利计划的既得利益者:福利津贴领取者,认为自己可以受益于福利计划的州和地方政府官员,而首先是管理福利计划的官僚。不那么明显的障碍是,福利改革的鼓吹者,包括现有的既得利益者,所要达到的目标互相冲突。
关于福利问题,马丁·安德森著有一本书,其中写得非常好的一章是“不可能彻底改革福利制度”,在这一章中他写道:
“所有彻底的福利改革计划都由三个政治上极为敏感的基本部分组成。第一是改革后基本的福利水平,例如为一个四口之家提供多少福利津贴。第二是改革计划在刺激接受福利津贴的人寻找工作和挣更多的钱方面将起什么作用。第三是改革是否会给纳税者带来额外的负担。
……改革计划要成为政治现实,必须在改革后仍然为现在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提供象样的补助,必须能强烈地刺激人们工作,而且给纳税者带来的负担必须是合理的。这三者必须同时兼顾。”
争论的焦点是怎样才算“象样”、“强烈”和“合理”,特别是怎样才算“象样”。如果“象样的”补贴意味着:现在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没有谁将因为改革而比当前少领津贴,那么,无论“强烈”和“合理”作何解释,也不可能同时达到上述三个目标。然而,正如安德森所说:“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国会决不会通过任何实际上会减少数百万福利津贴领取者所得的改革措施。”
让我们来看前一节中介绍的简单的负所得税制:一个四口之家的免征点是七千二百美元,按50%的补贴率计,凡没有收入来源的家庭可以得到三千六百美元的补助。50%的补贴率将给人以足够强烈的刺激去工作,而花费要比目前繁杂的福利计划省得多。但是,这种补贴标准今天在政治上是无法接受的。正如安德森所说:“现在(1978年初),美国典型的享受福利津贴的四口之家,每年可以得到大约六千美元的劳务和现金。在象纽约这样花销更大的州里,有些享受福利津贴的家庭每年得到的津贴在七千至一万二千美元之间,有的甚至更多。”
如果免征点定在七千二百美元,即便是收入六千美元的“典型”家庭,也需要有83.3%的补贴率。这样高的补贴率会严重地挫伤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同时大大增加开支。补贴率可以通过提高免征点来压低,但那又会极大地增加开支。这是一种无法解脱的恶性循环。要缩减从名目繁多的福利计划中得到高额福利津贴的人们的所得,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正如安德森所说:“我们不可能同时创造出进行彻底的福利改革所必需的全部政治条件。”
但是,今天政治上行不通,明天则可能行得通。在预言什么将成为政治上可行的事情上,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成绩非常糟。他们的预言一再被事实所否定。
我们的受人尊敬的伟大导师弗兰克·H·奈特喜欢用大雁由一只带头按人字形排队飞行的例子来说明不同的领导方式。他常说,当头雁一个劲儿地向前飞时,后面的大雁可能会飞向其他方向。头雁回头发现没有大雁跟随时,会赶紧掉头,重新带领人字形队伍朝前飞。这是一种领导方式。无疑,美国政府就常常采用这种方式。
我们承认,我们的建议目前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充分地说明我们的设想,不仅因为它是可以指导我们逐步进行改革的方针,而且还因为我们希望它终将成为在政治上可以办得到的事情。
结论
直到最近仍由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统治的王国,每年为我们的健康正在花费越来越多的钱。其主要结果只是增加医疗和保健费用,而医疗质量却没有任何相应的改进。教育经费也一直在激增,但教育质量却普遍地认为在下降。费用的上涨和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使我们不得不推行种族合校,而我们的社会看来却更为分崩离析。我们每年在福利事业上耗资数十亿美元。然而,在美国国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高的时候,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数却有增无减。社会保险的预算大得惊人,但社会保险却在财政上陷于严重的困境。年轻人颇有道理地抱怨,为接济老年人而要他们付的税太高。而老年人也颇有道理地抱怨,说他们无法维持被许诺的生活水平。制定的计划是要保证老年人不再成为救济对象,而看到的现实却是靠福利津贴生活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根据卫生、教育和福利部自己的计算,该部每年由于贪污受贿和铺张浪费损失的资金,足可以建造十万栋以上每栋耗资五万美元的住宅。
浪费是令人痛心的,但这不过是膨胀到这样大的家长式福利计划的祸害中最轻的一个。福利计划的主要祸害是对我们社会结构的影响。它们削弱家庭,降低人们对工作、储蓄和革新的兴趣,减少资本的积累,限制我们的自由。这些才是应当用来衡量福利计划的基本标准。
本节内容概述
从整个历史来看,这种转移在某种程度上早已存在了,以往青年人总是供养他们的父母或其他上了年纪的亲属。的确,在许多象印度那样有着很高死婴率的贫穷国家。养儿防老是造成高出生率和大家庭的主要原因。社会保险和早先供养父母的习惯的区别在于,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非个人的事情,而供养父母则是自己愿意的个人私事。道义的责任是个人而不是社会的事情。孩子照顾自己的父母是出于爱或责任感。现在,他们为供养别人的父母解囊是由于受到政府的强制和出于恐惧。早先的那种转移加强家庭的纽带,而强制的转移则削弱这种纽带。
如果负所得税制果真取代了各种福利计划,那将带来巨大的好处。该制度是专门用来对付贫困问题的。它将以最实用的形式,即用现金来资助接受者。它是综合性的,而不是因为接受者年纪大,有疾残,患病,或生活在某一地区,也不是因为任何其他使人们在现行福利制度下可以得到救济金的原因。它给予资助,是因为接受者收入低。它明白地规定由纳税人承担费用。象任何其他设法减少贫困的措施一样,它也会减少促使人们自助的刺激。但是,只要把补贴率限定在合理的水平上,它就不会完全消除这种刺激。因为多挣一块美元,总是意味着有更多的钱可花。
同样重要的是,负所得税制可以免除目前管理这一大堆福利计划的庞大官僚机构。负所得税可以直接成为现行所得税制的一部分,并且可以一起管理。由于每个人都要填报所得税单,它可以减少现行所得税制度下的逃税漏税现象。可能要增添一些人员,但增添的人决不会多于目前管理福利计划的人。
通过取消庞大的官僚机构,使补贴制与税收制相互结合,负所得税可以铲除目前的不正常现象,即一些人——掌管福利计划的官僚们——操纵着他人的生计。它将有助于消除当前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级的状况:纳税阶级和依靠政府救济过活的阶级。只要平衡点和税率定得合理,负所得税制将比我们现行的制度省钱得多。对于某些由于这样或那样原因无能力料理自己事务的家庭,给予个人帮助仍然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由负所得税来维持穷人家庭的收入,这种帮助可以,而且会由私人慈善活动来提供。我们认为,现行福利制度最大的代价之一在于,它不仅破坏家庭,而且减少私人慈善活动。
社会保险怎么能够实现这一在政治上总是行不通的美妙梦想呢?
依我们看,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实行负所得税制与逐步减少社会保险结合起来,同时继续履行现有的义务。其方法如下:
1.立即废除工资税。
2.按现行法律规定的数额,继续付给现在享受社会保险的人以应得的钱。
3.给予每个已经挣得保险的工人以享受退休、残废或遗属福利津贴的权利。这些福利金是工人根据现行的法律迄今已付的税款和所挣得的收入使他有权获得的,但要减去由于废除工资税而今后少缴纳的税款所折合的福利金数额。工人可以选择他所要的福利津贴的形式,可以是将来的一份年金,也可以是公债,其价值与按照目前规定他有权得到的福利津贴的价值相等。
4.给予每个尚未挣得保险的工人一笔钱(同样采取公债券的形式),数目等于他或他的雇主为他已缴纳的税款的累计价值。
5.停止积累保险津贴,让个人按自己的愿望为退休后安排养老。
6.从总的税收和政府发行的公债中为上述第2、3、4项开支提供资金。这样一个过渡性纲领丝毫不会增加美国政府的实际债务。相反,它会由于不再向未来的福利津贴接受者许诺而减少债务。它只是把现在隐蔽的债务公开化。它为现在未备基金的计划提供资金。这些步骤会导致大多数现存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立即解散。逐步减少社会保险,将消除目前社会保险制度给就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意味着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它将增加个人储蓄,从而导致更高的资本形成率和更快的收入增长率。它将刺激私人养老金计划的发展和扩大,从而使许多工人感到生活更有保障。
浪费是令人痛心的,但这不过是膨胀到这样大的家长式福利计划的祸害中最轻的一个。福利计划的主要祸害是对我们社会结构的影响。它们削弱家庭,降低人们对工作、储蓄和革新的兴趣,减少资本的积累,限制我们的自由。这些才是应当用来衡量福利计划的基本标准。
附录UBI和负所得税
弗里德曼提倡UBI是为了方便取消庞大的福利保障体系,我们这种负福利地区用不上这种方式。
附录【吴钩】《官办救济的困境》
作者:吴钩
来源:《华商报》2012-12-15
中国各代有各种官办的救济机构,初衷是为济贫救困、赈灾恤民,但权力的深度介入、官僚化的运作,日久都免不了弊病丛生,不但恤不了民,甚至成为“害民”之政。旧时常平仓、义仓与社仓的蜕变过程,给予后人一次又一次的教训。
常平仓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建制化官办公益机构(之一),汉代时已有常平仓之设置。所谓“常平”,乃是指“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以平抑物价。另外,常平仓也具有政府救济的功能,“如遇凶荒,即按数给散灾民贫户”。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罗斯福政府实行新政,还曾将常平仓思想引入美国农业立法。——按钱穆先生的说法,“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王安石)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担任过美国农业部长的华莱士也承认,“我接任农业部长后,在最快的时间内敦促国会通过立法,把中国古代农业政治家的实践——‘常平仓’引入美国农业立法中。”
从初衷看,常平仓不可谓不是“良法”。然而,历史的经验表明,任何官办机构几乎都免不了被权力异化,常平仓施行日久,也沦为“吏以为市,垄断渔利”之法。汉元帝时,诸儒提出毋与民争利,请罢常平仓。东汉明帝又拟设置常平仓,有官员即以常平仓“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为由,反对复置常平仓。从汉至清,常平仓的弊病几乎是定期发作的。
义仓出现的时间晚于常平仓,始见于隋朝:由官府“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之后唐太宗又将义仓之法加以完善、推广,规定“王公已下垦田,亩纳二升”,“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常平仓之粮出于官,而义仓之粮出于民,由政府强制征收,代为管理,类似于某种强制保险。
在官府力推之下,大唐“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谨,则开仓赈给”,义仓良法,看起来很美。然而,很快,义仓之粮便被官府挪作他用,“其后公私窘迫,渐贷义仓支用,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后世见识过社保基金被政府部门挪用来填补财政窟窿的人,对此应该不会感到意外。
义仓之败坏,其害甚于常平仓。原因宋人已说得很清楚了:“常平出于官,义仓出于民。出于官者,官自敛之,其弊虽不足以利民,亦不至于病民。出于民者,民实出之,官实敛之,其敛不但民无给,而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为常赋。”义仓之法,最后变成官府加税的名目,人民不但得不到救济,反而被强加了负担。
社仓是传统社会的NGO。第一个社仓由南宋士绅魏掞之1150年创立于福建招贤里。稍后(1168年),魏掞之的好友朱熹也在五夫里设立社仓。宋儒设置社仓的初衷,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的官方救济如常平仓不尽可靠,那么士绅就应当担起造福乡里之责,建立民间的自我救济体系,这样,乡人遇到凶岁饥荒时就不必全然依赖有司了。
社仓类似于今日社会贤达所办理的农村小额扶贫信贷,每年在青黄不接的五月份放贷,借米的人户则在收成后的冬季纳还本息。与青苗法不同,社仓由地方士绅组织并管理,人户是否要借贷也采取自愿原则,“如人户不愿请贷,亦不得妄有抑勒”。抑勒,就是强制、摊派之意。在朱熹的规划中,特别强调了社仓运作应独立于官方权力系统之外,不受官府干预。
1181年,朱熹上奏朝廷,建议在全国推行社仓之法。宋孝宗采纳了朱熹之议,下诏推广社仓,四五十年下来,朱子社仓“落落布天下”。然而,在社仓获得官府青睐的过程中,随着国家权力的介入越来越深,这一NGO组织也慢慢变质,最后居然成了“领以县官,主以案吏”的官办机构,并且跟青苗法一样暴露出“害民”的弊病,渐渐沦为害民之法,“非蠧于官吏,则蠧于豪家”。值得指出的是,“蠧于官吏”的危害无疑更甚于“蠧于豪家”,因为官吏掌握着“豪家”所没有的国家权力。时人俞文豹描述了南宋晚期社仓“蠧于官吏”的情形:一方面官府强制征收仓米,另一方面又将仓米挪作他用,即使遇到荒年,也“未尝给散”。民间公益给权力一插手,就变得乌烟瘴气了。
南宋末,朱熹的“再传弟子”黄震对官办的广德军社仓进行了“国退民进”的改革,“请照本法(朱子社仓之法)一切归之民”,即恢复社仓的NGO本色,委任地方士绅掌管仓米的借贷,官方只负责监督社仓“照官秤公平出贷”,而不准插手社仓的具体运作。黄震的社仓改革方向当然是对的。宋代社仓原本就是由士绅发起于民间、并且在士绅主持下运作良好的社会自组织,又何必要官府插上一脚?
社仓发展到清代时,又由于受政府控制,也出现了“蠧于官吏”的弊病:“近来官为经理,大半皆藉挪移,日久并不归款,设有存余,管理之首事与胥吏亦得从中盗卖”。到清代后期,由于社仓已荒废,不可修补,又有士绅出来“募捐田亩”,购置房屋设立义仓,“办理积仓备荒”。这里的“义仓”,为绅办,已不同于隋唐时期的官办义仓。这是义仓的再生。
现在,我们回头看看常平仓、义仓、社仓的兴衰轨迹,似乎可以得出一个道理:官办的公益救济,虽然从其初衷看,是“利民之良法”,但只要运行日久,几乎都无可避免地沦为“害民之恶法”。另一方面,面对官办机构的缺陷或败坏,儒家士君子也有足够的热情与技艺组织民间结社互助,主持NGO的良性运行。这才是中国传统社会得以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附录【吴钩】《宋王朝的国家福利与“福利病”》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赐稿
摘自 吴多纳新书《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
许多人可能都会以为,现代国家福利制度起源于1601年英国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这部法典将贫困人口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值得救济的穷人”,包括年老及丧失劳动力的残疾人、失去依靠的儿童,教区负有救济他们的责任,如给成年人提供救济金、衣物和工作,将贫穷儿童送到指定的人家寄养,待长到一定年龄时再送去当学徒工;另一类是“不值得被救济的人”,包括流浪汉、乞丐,他们将被关进监狱或送入教养院,接受强制劳动。
一些学者会告诉你,《伊丽莎白济贫法》的颁行,意味着英国“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社会救助制度”。这么言之凿凿的人,肯定不知道,也想象不到,比《伊丽莎白济贫法》更完备、更富人道主义精神的福利救济制度,实际上早在11~13世纪已经出现于宋代中国。
不相信吗?请跟着13世纪意大利的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到杭州看看南宋遗留下来的福利机构。马可·波罗在到达杭州之前,听说宋朝设有一种福利性的育婴机构:“诸州小民之不能养其婴儿者,产后即弃,国王尽收养之。记录各儿出生时之十二生肖以及日曜,旋在数处命人乳哺之。如有富人无子者,请求国王赐给孤儿,其数惟意所欲。诸儿长大成人,国王为之婚配,赐之俾其存活,由是每年所养男女有二万人。”
等到他来到杭州时,已经元朝了,杭州的育婴机构早已荒废多时。不过,他看到了另一种叫做“养济院”的福利机构:“日间若在街市见有残废穷苦不能工作之人,送至养济院中收容。此种养济院甚多,旧日国王所立,资产甚巨。其人疾愈以后,应使之有事可作。”
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有疑问:马可·波罗的记述可靠吗?
国家福利
我们不妨以宋朝人自己的记录为参证。吴自牧《梦粱录》载,“宋朝行都于杭,若军若民,生者死者,皆蒙雨露之恩”——
1)“民有疾病,州府置施药局于戒子桥西,委官监督,依方修制丸散【口父】咀,来者诊视,详其病源,给药医治,……或民以病状投局,则畀之药,必奏更生之效”;
2)“局侧有局名慈幼,官给钱典雇乳妇,养在局中,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无力抚养,抛弃于街坊,官收归局养之,月给钱米绢布,使其饱暖,养育成人,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
3)“老疾孤寡、贫乏不能自存及丐者等人,州县陈请于朝,即委钱塘、仁和县官,以病坊改作养济院,籍家姓名,每名官给钱米赡之”;
4)“更有两县置漏泽园一十二所,寺庵寄留槥椟无主者,或暴露遗骸,俱瘗其中,仍置屋以为春秋祭奠,听其亲属享祀,官府委德行僧二员主管”。
《梦粱录》所载者,是宋政府针对贫困人口而设立的四套福利系统:1)施药局为医药机构,代表医疗福利;2)慈幼局为福利孤儿院,代表儿童福利;3)养济院为福利养老院,代表养老福利;4)漏泽园为福利公墓,代表殡葬福利。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南宋时的杭州参观,走到戒子桥西,便可以看到施药局,旁边则是慈幼局,马可·波罗听闻的福利育婴机构,便是慈幼局。
这些福利机构并非仅仅设于都城杭州。北宋后期,朝廷已经要求“诸城、寨、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凡户口达到千户以上的城寨镇市,都必须设立居养院(即养济院)、安济坊、漏泽园,更别说人口更集中的州县城市了。南宋时,一些州县又创设了收养弃婴与孤儿的慈幼局,宝祐四年(1256),宋理宗下诏要求“天下诸州建慈幼局”,将慈幼机构推广至各州县。
宋理宗还说了一个心愿:“必使道路无啼饥之童。”至少在京畿一带,这位君主的理想已得以实现,因为一名元朝文人说:“宋京畿各郡门有慈幼局。盖以贫家子多,辄厌而不育,乃许其抱至局,书生年月日时,局设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无子女,许来局中取去为后。故遇岁侵,贫家子女多入慈幼局。是以道无抛弃之子女。若冬遇积雨雪,亦有赐钱例。虽小惠,然无甚贫者。此宋之所以厚养于民,而惠泽之周也。”这一记录,也可以证明马可·波罗所言不虚。
北宋时期虽然尚未出现专设的慈幼局,不过已有针对孤儿、弃婴的救济,宋徽宗曾诏令居养院同时收养孤儿:“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其衣襕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遗弃小儿,雇人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
南宋初,宋高宗又下诏推行“胎养助产令”:“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婴者,给钱养之。”给钱的标准是:“应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户,及无等第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于常平钱内,人支四贯文省”,符合救助条件的家庭,生育一名婴儿可获政府补助4贯“奶粉钱”。宋孝宗时又改为“每生一子,给常平米一硕、钱一贯,助其养育”。许多州县还设有地方性的“举子仓”,由地方政府向贫家产妇发放救济粮,一般标准是“遇民户生产,人给米一石”。
如果说,胎养令、举子仓与慈幼局代表了宋朝贫民“生有所育”的福利,养济院的出现则反映了宋人“老有所养”的福利。养济院是收养鳏寡、孤独、贫困老人的福利院,北宋时称为“居养院”,创建于元符元年(1098),这年宋哲宗下诏:“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崇宁五年(1106),宋徽宗赐名“居养院”,南宋时则多以“养济院”命名。
按宋人习惯,“六十为老”,年满60岁的老人,若属鳏寡、孤独、贫困,老无所依,居养院即有义务收养。宋徽宗时还一度将福利养老的年龄调低到50岁:“居养鳏寡孤独之人,其老者并年满五十岁以上,许行收养,诸路依此。”按北宋后期居养院的救济标准,“应居养人,日给粳米或粟米一升、钱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钱五文省”。
宋人还有“病有所医”的福利——体现为福利药局与福利医院的设置。熙宁变法期间,宋政府成立了营利性的合卖药所,宋徽宗将它改造成福利性的和剂局、惠民局,南宋相沿,行在临安与地方州县均设有官药局。官药局类似于现在的平价门诊部、平价大药房,如江东提刑司拨官本百万,开设药局,“制急于民用,……民有疾咸得赴局就医,切脉约药以归”;建康府的惠民药局,“四铺发药,应济军民,收本钱不取息”;临安府的施药局,“其药价比之时直损三之一,每岁糜户部缗钱数十万,朝廷举以偿之”,施药局诊病配药,药价只收市场价的三分之二,由户部发给补贴。有时候,施药局也向贫困人家开放义诊,并免费提供药物。
除了官药局,宋代还设有福利医院,即安济坊。安济坊配备有专门的医护人员,每年都要进行考核:“安济坊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疗痊失,岁终考会人数,以为殿最,仍立定赏罚条格。”病人在安济坊可获得免费的救治和伙食,并实行病人隔离制,以防止传染:“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又作厨舍,以为汤药饮食人宿舍。”
此外,宋朝的一些地方政府还设立了安乐庐,这是针对流动人口的免费救治机构。如南宋时,建康府人口流动频繁,常常有旅人“有病于道途,既无家可归,客店又不停者,无医无药,倾于非命,极为可念”,政府便设立安乐庐,凡“行旅在途”之人,发现身有疾病后均可向安乐庐求医,“全活者不胜计”。
人生的起点是摇篮,人生的归宿是坟墓,最后我们还要看看宋朝在“死有所葬”方面的福利。历朝官府都有设义冢助葬贫民、流民的善政,但制度化的福利公墓建设要到北宋后期才出现,宋徽宗要求各州县都要建造福利公墓,取名“漏泽园”:“凡寺观旅梓二十年无亲属、及死人之不知姓名、及乞丐或遗骸暴露者,令州县命僧主之,择高原不毛之土收葬,名漏泽园”。蔡京政府对漏泽园的建设尤为得力。
漏泽园有一套非常注重逝者尊严的制度:“应葬者,人给地八尺、方砖二口,以元寄所在及月日、姓名若其子娉、父母、兄弟、今葬字号、年月日,悉镌讫砖上,立峰记识如上法。无棺柩者,官给。已葬而子娉亲属识认,今乞改葬者,官为开葬,验籍给付。军民贫乏,亲属愿葬漏泽园者,听指占葬地,给地九尺。无故若放牧,悉不得入。仍于中量置屋,以为祭奠之所,听亲属享祭追荐。”
根据这段记载,可以知道,漏泽园的坟墓有统一规格,约八尺见方,以两块大方砖铭刻逝者的姓名、籍贯、生辰、安葬日期,有亲属信息的,也刻于砖上,作为标记。没有棺木的逝者,政府给予棺木收殓;已在漏泽园安葬者,如果有亲属愿意迁葬他处,政府将给予方便;贫困家庭的亲人去世后想安葬于漏泽园的,政府也允许——当然,不用收费。漏泽园设有房屋,以便逝者的亲属来此祭祀。
总而言之,对于贫困人口,宋朝政府试图给予“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关怀,提供的基本福利涵盖了对“生老病死”的救济。宋徽宗曾毫不谦虚地说:“鳏寡孤独,古之穷民,生者养之,病者药之,死者葬之,惠亦厚矣。”宋代福利之发达,不管跟后来的元明清时期相比,还是与近代化刚刚开始时的欧洲国家相较,都堪称领先一步。
过度福利
更有意思的是,宋朝“济贫政策所引发的关注及批评,已有类似近代国家福利政策之处”。近代国家常见的从福利政策衍生出来的“福利病”,同样存在于宋朝。请注意,我们要说的宋朝“福利病”,是指国家福利制度的衍生问题,而不是管理不善或制度漏洞所导致的弊病。
正如我们在一些福利国家所看到的情形,宋朝政府的福利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也诱发了“过度福利”的问题。宋徽宗的诏书一再指出过这个问题。
大观三年(1109)四月,宋徽宗在一份手诏上说:“居养、安济、漏泽,为仁政先,欲鳏寡孤独养生送死各不失所而已。闻诸县奉行太过,甚者至于许供张,备酒馔,不无苛扰。”有些州县的福利机构为救济对象提供酒馔,待遇不可谓不优厚。皇帝要求有司纠正这股“过度福利”之风:“立法禁止,无令过有姑息。”
次年,即大观四年八月,徽宗重申:“比年有司蹑望,殊失本指。至或置蚊帐,给肉食,许祭醮,功赠典,日用即广,縻费无艺。”诏令各州县停止福利扩张与靡费铺张,除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之外,不要自行设置其他的福利机构。
十年后,即宣和二年(1120)六月,宋徽宗再次下诏批评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资给过厚”的做法:“居养、安济、漏泽之法,本以施惠困穷。有司不明先帝之法,奉行失当,如给衣被器用,专雇乳母及女使之类,皆资给过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居养院与安济坊不但免费提供一切日常用具,还替接受救济的人雇请了乳母、保姆与陪护,以致政府的财政拨款入不敷出。
《嘉泰会稽志》也记载说,“居养院最侈,至有为屋三十间者。初,遇寒惟给纸衣及薪,久之,冬为火室给炭,夏为凉棚,什器饰以金漆,茵被悉用毡帛,妇人、小儿置女使及乳母。有司先给居养、安济等用度,而兵食顾在后。”
这种“縻费无艺”的“过度福利”,显然跟制度缺陷、监管不力造成的“福利腐败”并非同一回事。宋代的福利机构当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不过那是另一个话题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宋代“过度福利”,与其说是福利腐败,不如说跟政府的施政偏好密切相关。
宋朝福利的鼎盛期是蔡京执政的时期。为什么蔡京那么热衷于推行福利政策?因为他是新党领袖王安石的继承人,用现在的话语来说,北宋新党具有鲜明的左派风格,他们推动变法的目标之一便是“振乏绝,抑兼并”,希望运用国家的强制力与财政资源,救济贫困人口,抑制兼并,防止贫富分化悬殊。
蔡京拜相执政之年,宋徽宗将年号“建中靖国”改为“崇宁”,即意味着君臣宣告终止之前调和左右的折中政治,恢复熙宁变法的左翼路线。蔡京政府也确实以“振乏绝,抑兼并”为己任。蔡氏曾经告诉徽宗:“自开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贸易,富者恃其有余,厚立价以规利;贫者迫于不足,薄移税以速售,而天下之赋调不平久矣。”表达了对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的关切。后来蔡京下台,接任的宰相王黼“阳顺人心,悉反蔡京所为”,其中就包括“富户科抑一切蠲除之”,这反证了蔡京执政时实行过“科抑富户”的左翼政策。
也因此,蔡京一上台执政,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的建设便迅速在全国铺开,乃至出现“过度福利”。而当蔡京罢相时,宋朝的福利制度又会发生收缩,如大观四年、宣和二年,皇帝下诏纠正“过度福利”,都是蔡京罢相之时。
养懒汉
我们现在都说,优厚的福利制度下,很容易“养懒汉”。在蔡京执政之际、北宋福利制度迅速扩张的时期,确实出现了“养懒汉”的问题,比如一些州县的居养院和安济坊,由于政府提供的生活条件非常不错,“置蚊帐,给肉食”,甚至还有保姆、做家政的阿姨,所以便有“少且壮者,游惰无图,廪食自若,官弗之察,弊孰甚焉”,在居养院或安济坊中赖着不走,白吃白喝白睡。
许多到过西欧国家旅游的人都会发现,高福利制度已经深刻塑造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节奏:每天工作几小时,要么就成天晒太阳,经常休假旅游,大街上很少看到行色匆匆的上班族。这种图享乐、慢节奏的生活风气,也出现在南宋时的杭州社会。
如果马可·波罗在南宋时就来到杭州,他将会看到,西湖一带,“湖山游人,至暮不绝。大抵杭州胜景,全在西湖,他郡无此,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乐事之时,讵宜虚度?至如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终日游玩的人,不但有“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这等富贵子弟,还有“解质借兑”(类似于今日城市刚刚兴起的“贷款旅游”)的城市贫民,“不特富家巨室为然,虽贫乏之人,亦且对时行乐也”。
这些贫乏的市民为什么能够“对时行乐”,乃至敢于“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怕饿死么?不怕。因为南宋杭州市民享受到的福利非常丰厚。
请看周密《武林旧事》的记载:“都民素骄,非惟风俗所致,盖生长辇下,势使之然。若住屋则动蠲公私房赁,或终岁不偿一钚。诸务税息,亦多蠲放,有连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认。诸项窠名,恩赏则有‘黄榜钱’,雪降则有‘雪寒钱’,久雨久晴则又有‘赈恤钱米’,大家富室则又随时有所资给,大官拜命则有所谓‘抢节钱’,病者则有施药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则有慈幼局,贫而无依者则有养济院,死而无殓者则有漏泽园。民生何其幸欤。”
南宋杭州市民所享受到的政府福利(私人慈善不计在内)包括:减免赋税,经常蠲免房屋租金;遇上大节庆,政府会发“黄榜钱”,碰上大雪天,发“雪寒钱”,久雨久旱则发放“赈恤钱米”;贫困的病人可到施药局免费诊治取药,被遗弃的孤儿会被收养入慈幼局,贫而无依之人送入养济院养老,死而无殓者安葬在漏泽园。
——换成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福利制度下,即使身无分文,也是敢“贷款旅游”,带着老婆孩子玩个痛快的。对不?
贫者乐而富者扰
福利制度看起来很诱人,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羊毛最终出在羊身上,不是出在这群羊身上,便是出在那群羊身上。宋政府维持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福利机构运转的经费,有几个来源:左藏库,即国家财政拨款;内藏钱,皇室经费的资助;公田的租息收入;国营商业机构的收入,比如“僦舍钱”,即官营货栈的租金收入;常平仓的利息钱米。其中常平仓的息钱为大头。如果常平仓息钱不足用,通常就只能挪用其他用途的财政款项或者增加税收了。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述了崇宁年间各州县倾财政之力办理福利救济的情形:“崇宁间初兴学校,州郡建学,聚学粮,日不暇给。士人入辟雍,皆给券,一日不可缓,缓则谓之害学政,议罚不少贷。已而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谚曰:‘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盖军粮乏,民力穷,皆不问,若安济等有不及,则被罪也。”以蔡京政府的施政偏好,救济贫民的福利支出优先于军费开销。军粮缺乏,可以容忍;济贫不力,则会被问责。
这并非陆游的虚构,因为徽宗的诏书可以佐证。宣和二年六月十九日,皇帝诏曰: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救济过度,“常平所入,殆不能支。天下穷民饱食暖衣,犹有余峙;而使军旅之士稞食不继,或至逋逃四方,非所以为政之道”。难怪当时的民谚要讥笑蔡京政府“不养健儿,却养乞儿”。
这是占用财政拨款的情况。宋徽宗的诏书还提到因“过度福利”而导致民间税负加重的问题:大观三年四月二日,皇帝手诏:“闻诸县奉行(福利救济)太过,甚者至于许供张,备酒馔,不无苛扰。”这里的“苛扰”,便指政府增税,骚扰民间。《宋史·食货志》也称,蔡京时代的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糜费无艺,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率敛”也是增税的意思。由于宋代的赋税主要由富户承担,而福利机构的救济对象为贫民,所以便出现“贫者乐而富者扰”之讥。
洪迈《夷坚志》中有一则“优伶箴戏”的故事,辛辣讽刺了蔡京时代“贫者乐而富者扰”的福利制度。故事说,三名杂剧伶人在内廷表演滑稽戏时,饰演成儒生、道士与僧人,各自解说其教义。
儒生先说:“吾之所学,仁义礼智信,曰‘五常’。”然后采引经书,阐述“五常”之大义。道士接着说:“吾之所学,金木水火土,曰‘五行’。”亦引经据典,夸说教义。
轮到僧人说话,只见他双掌合十,说道:“你们两个,腐生常谈,不足听。吾之所学,生老病死苦,曰‘五化’。藏经渊奥,非汝等所得闻,当以现世佛菩萨法理之妙为汝陈之。不服,请问我。”
儒生与道人便问他:“何谓生?”僧人说:“(如今)内自太学辟雍,外至下州偏县,凡秀才读书,尽为三舍生。华屋美馔,月书季考;三岁大比,脱白挂绿,上可以为卿相。国家之于生也如此。”(这里的“生”,伶人理解为“书生”,指的是国家的教育福利,恰可弥补我们前述所未及之处。)
又问:“何谓老?”僧人说:“(昔者)老而孤独贫困,必沦沟壑。今所在立孤老院,养之终身。国家之于老也如此。”
又问:“何谓病?”僧人说:“(生民)不幸而有病,家贫不能拯疗,于是有安济坊,使之存处,差医付药,责以十全之效。其于病也如此。”
又问:“何谓死?”僧人说:“死者,人所不免,唯穷民无所归,则择空隙地为漏泽园;无以殓,则与之棺,使得葬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其于死也如此。”
最后问:“何谓苦?”僧人“瞑目不应”,神情很是悲苦。儒生与道人催促再三,僧人才“蹙额”答道:“只是百姓一般受无量苦。”
教坊杂剧伶人表演这出滑稽戏,是想告诉皇帝,政府为维持庞大的福利支出,变着法子加税,已经使老百姓“受无量苦”了。看演出的宋徽宗听后,“恻然长思”,倒也没有怪罪讥讽时政的伶人。
为什么是宋朝?
在宋朝济贫政策的推行过程中,特别是在蔡京政府的“福利扩张”时期,“福利病”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这一点无可讳言。不过,有一个道理我认为也需要指出来:“过度福利”好比是“营养过剩”,一个营养不良的人是不应该担心营养过剩的;如果因为担心营养过剩而不肯吃肉,那就是跟“因噎废食”差不多的愚蠢了。
宋人的态度比较务实——既不齿于蔡京的为人,也抨击过“资给过厚”的“过度福利”,但对蔡京政府推行的福利制度本身,却是很赞赏,朱熹说:崇宁、大观之间,“始诏州县立安济坊、居养院,以收恤疾病癃老之人,德至渥矣。”甚至有宋人相信,蔡京为六贼之首,独免诛戮,乃是因为他执政之时,“建居养、安济、漏泽,贫有养,病有医,死有葬,阴德及物所致”。可见宋人只是反感“过度福利”,并不拒绝福利制度。
而在宋朝之外的朝代,我们就很难见到关于“福利病”的记载了。这当然不是因为其他王朝的福利制度更加完善,而是因为,宋朝之外的王朝,政府并未积极介入对贫困人口的救济,没有建立完备的福利救济机构。
尽管《周礼》中载有“保息六政”: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管子》中亦记录有“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但这只是带有福利色彩的政策,没有证据显示当时已设立了专门的福利机构。
南北朝时,南齐出现了免费收治贫病之人的“六疾馆”,北魏建立了功能相似的病坊,南梁则设有收养孤老与孤儿的“孤独园”,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福利机构,但不管是“六疾馆”,还是“孤独园”,全国只有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用。而且,建“六疾馆”的南齐太子萧长懋,建“孤独园”的南梁皇帝萧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准确地说,他们是以佛教徒(而非国君)的身份修建福利机构的。政府并没有创设福利制度的自觉。
唐代从京师到一些地方都出现了“悲田养病坊”,负责收养贫病孤寡,有时也收留流浪乞丐,但悲田养病坊是从寺院中发展起来的,日常工作也由僧人主持,“悲田”二字即来自佛经,唐政府只是给予资助并参与监督,与其说它是国家福利机构,不如说是民间慈善组织。
宋朝之后的元明清三朝,国家福利也出现了明显的退缩。我们知道,宋代的贫民福利体系包括四个系统:1)以官药局和安济坊为代表的医疗福利;2)以胎养令和慈幼局为代表的生育福利;3)以居养院或养济院为代表的养老福利;4)以漏泽园为代表的殡葬福利。恰好囊括了对贫民“生老病死”的救济。
这四个福利系统,除了医药救济得到元政府的重视之外,其他福利机构在元朝都被废弃了;明朝的朱元璋虽然重建了惠民药局与养济院两套系统,但惠民药局在明中期之后基本上已经荒废,“养济院”则被用于控制人口流动,因为明政府规定:街上的流浪乞丐要送入养济院收容,候天气和暖,再遣送回原籍;清王朝只保留了养济院的设置,并且同样利用养济院系统控制流民,至于对弃婴、孤儿的救济,则被清廷视为是“妇女慈仁之类,非急务也”。
总而言之,宋朝政府建立的“从摇篮到坟墓”全覆盖的贫民福利体系,我们在其他王朝是找不到的。没有发达的福利体系,又哪来衍生的“福利病”?
那么,为什么只有宋王朝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贫民福利制度的建设?你可能会说,因为宋朝皇帝推崇儒家的“仁政”。但哪一个朝代的君主不是以“推行仁政”相标榜呢?为什么他们在实际行动上又提不起兴建福利机构的劲头?
我读过历史学者梁其姿的大著《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受其启发,想提出一点综合的解释。
宋代福利制度的建立,首先是近代化产生的压力催化出来的结果。研究者发现,在16世纪的欧洲,当社会经济结构从封建制度过渡至资本主义制度之际,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个后果:由于社会经济急剧变化,大量都市贫民被“制造”出来,成为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近代欧洲国家逐渐发展出来的福利政策,其实就是为了应对这一崭新的社会问题。英国政府制订“济贫法”之举,即始于近代化正在展开的16世纪下半叶,及至17世纪初,便诞生了完备的《伊丽莎白济贫法》。“济贫法”的出现,意味着英国政府开始负担起救济贫民的责任,在此之前,英国的济贫工作主要是由教会承担的。
中国则在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大变革,历史学家们相信,唐朝是“中世纪的黄昏”,宋朝则是“现代的拂晓时辰”,伴随着均田制的解体、贵族门阀的消亡、商品经济的兴起、人口流动的频繁、“不抑兼并”与“田制不立”政策的确立,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催生了大量的都市贫困人口,传统的由宗教团体负责的慈善救济已不足以应对都市贫困问题,政府需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提供更周全的救济。而“官方的长期济贫机构在宋亡后约三百多年间没有进一步发展,反而萎缩,这当然并不说明元明间的贫穷问题减轻了,而是这三百年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没有如宋代一样使都市贫穷成为突出的问题”。
其次,宋朝福利制度的建立也是“大政府”政策取向的结果。纵览历史,我们会发现,宋王朝有着显著的“大政府”性格,政府不但设置了大量的经济部门介入商业活动,开拓市场,对涌现出来的都市贫困问题,也是倾向于以国家力量积极解决,不仅建立了针对贫民“生老病死”问题的福利救济机构,而且在政府的施政过程中,还出现了接近现代意义的“贫困线”概念(之前的王朝是不存在一条一般性的“贫困线”的):田产20亩以下或者产业50贯以下的家庭,即为生活在贫困线下的“贫弱之家”、“贫下之民”。贫民可以享有一系列政策倾斜与政府救济,如免纳“免役钱”,免服保甲之役,获得“胎养助产”补助,借贷常平米钱免息,发生灾荒时优先得到救济,等等。
为什么宋朝建立的绝大多数福利机构都在元朝消失了?一个不容忽略的原因便是,“此后的中央政府不似宋代的积极”。特别是朱元璋缔造的明王朝,更是表现出鲜明的“小政府”性格,国家财政内敛,公权力消极无为,政府职能严重萎缩,晚明之时,当都市贫困再次成为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朝廷依然缺乏兴趣去规划建设一个完整的福利体系。梁其姿总结说:“在政治理念方面,明政权又缺乏宋代的创意。明政府并不曾制定一套长期性的、全国性的社会救济政策。”这个评价是精准的,不过我们还要补充一句:以明王朝的内敛型财政,即便朝廷有心,也无力发展宋朝式的福利制度。清承明制,清王朝差不多也是如此。
不过,从晚明开始,由地方士绅主导的民间慈善力量已发育成熟,“既然政府并不正视新富及贫穷所带来的社会焦虑,地方精英自然而然地接手处理这个问题”。这便是自晚明至晚清期间,善会、善堂等民间慈善组织勃兴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要等到16世纪下半叶,随着英国“济贫法”的出台,政府救济机构的建立,国家才承担起向贫民提供救济的义务,之后,英国的福利制度慢慢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显然离不开重商主义财政的支撑。而中国在宋朝之后,囿于“小政府”的惰性,福利制度建设非但裹足不前,且比宋朝退步了,此消彼长,到晚清时,便完全落后于英国。
游历海外的晚清学者王韬发现,英国政府所征之税,“田赋之外,商税为重。其所抽虽若繁琐,而每岁量出以为入,一切善堂经费以及桥梁道路,悉皆拨自官库,藉以养民而便民,故取诸民而民不怨,奉诸君而君无私焉。国中之鳏寡孤独、废疾老弱,无不有养。凡入一境,其地方官必来告曰,若者为何堂,若者为何院,其中一切供给无不周备。盲聋残缺者,亦能使之各事其事,罔有一夫之失所。呜呼!其待民可谓厚矣。”如此情景,仿佛就是中国宋朝。
宋朝的福利制度尽管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包括福利制度衍生的“福利病”、由于监管不力而产生的“福利腐败”,等等,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否则福利制度,一个没有基本福利“兜底”的社会,是不可能安宁的。两宋天灾频仍,据学者的研究,其发生灾害的“频度之密,盖与唐代相若,而其强度与广度则更有过之”。宋代的民变也此起彼伏,300余年出现400多起民变,不过都是小股民变,很快平息,如果宋朝没有这么一个覆盖面广泛的国家福利系统,恐怕民变早就一发不可收拾。要知道,两宋可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发生全国性民变的长命王朝,这里面,应有国家福利“兜底”之功。
南宋诗人楼钥写过一首讲述家史的长诗《次韵雷知院观音诗因叙家中铜像之详》,里面有一句是这么说的:“衰宗幸有此奇特,信知福利非唐捐。”用这一诗句形容宋朝的福利制度,也是很恰切的。
附录【吴钩】《台风“山竹”过后,我们来谈谈宋朝人怎样运用经济学赈灾》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八月初九日癸丑
耶稣2018年9月18日
今年特大台风“山竹”来临之时,我正好在家乡近海小城,目击台风呼啸而过。又看到网友留言:“期待吴老师写一期大宋朝时候的台风灾害及赈灾”。那就来说说宋朝的台风与赈灾吧。
十一至十三世纪的宋王朝,由于恰好横跨了两个气候温暖期,中间还夹着一个寒冷期,气候变化频繁,导致自然灾害的出现也更加密集,两宋三百余年,单就史有记录的水灾,便有600多次。宋朝史料记载的台风,也是触目惊心,看样子比“山竹”还要厉害。
太平兴国七年八月,琼州飓风,坏城门、州署、民舍殆尽。九月,太平军飓风拔木,坏廨宇、民舍千八十七区。十月,雷州飓风坏禀库、民舍七百区。九年八月,白州(博白)飓风,坏廨宇、民舍。
乾道二年八月,温州大风,海溢,漂民庐、盐场、龙朔寺,覆舟,溺死二万余人,江滨胔骼尚七千余。
乾道五年夏秋,温、台州凡三大风,水漂民庐,坏田稼,入畜溺死者甚众,黄岩县为甚,郡守王之望、陈岩肖不以闻,皆黜削。
淳熙三年八月,台州大风雨,至于壬午,海涛、溪流合激为大水,决江岸,坏民庐,溺死者甚众。
庆元元年六月,台州及属县大风雨,山洪、海涛并作,漂没田庐无算,死者蔽川,漂沉旬日。
由于天灾频仍,宋朝的荒政也很完备,中国第一部救荒专书《救荒活民书》,便诞生在南宋。
宋代比较有现代气息的赈灾模式,表现为市场逻辑的崛起,政府有意识地运用市场机制赈济灾民,这其中的佼佼者,当推北宋名臣范仲淹与赵抃。
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皇祐二年(1050年),两浙路发生灾荒,“吴中大饥,殍殣枕路”,当时范仲淹为杭州知州,兼负责浙西一带的赈灾。范仲淹除了给饥民“发粟”之外,见“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便“纵民竞渡”,鼓励民间多办些赛龙舟活动,鼓励居民出游观看比赛。他自己则每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又叫来杭州的“诸佛寺主首”,告诉他们:“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诸寺主首觉得有道理,于是大兴土木,雇佣了许多工人。杭州政府也大举兴建“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
范仲淹的做法很快引起监察系统的注意,浙西路的监司弹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这也说明当时的监察系统反应灵敏、运作正常,如果无人出来弹劾,那才不正常)。范仲淹坦然处之。朝廷派人一调查,发现范仲淹之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范公的举措,恰好暗合了凯恩斯的理论,即通过扩大投资与鼓励消费来拉动经济,从而惠及民生。当时杭州的“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这无数人,都因为范仲淹施行的“凯恩斯经济刺激政策”,而不致失业、沦为流民。那一年,“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沈括赞扬说,此皆“先生之美泽也”。
二十年后的熙宁八年(1075年),两浙路又有灾荒,“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诸州政府为平抑粮价,皆在“衢路立告赏,禁人增米价”。米价虽然控制住了,但市场上却没有多少米可以出售。当时在越州(今绍兴)任太守的赵抃,则反其道而行之,命人贴出公告,宣布政府不抑粮价,有多余粮食之人尽管“增价粜之”,想卖多少价钱就卖多少价钱。如此一来,各地米商见有利可图,纷纷运米前往越州,很快越州的商品粮供应充足,米价也跌了下来。
这则故事记录在明代冯梦龙编撰的《智囊全集》中。冯梦龙讲完故事后评论说:“大凡物多则贱,少则贵。不求贱而求多,(赵抃)真晓人也。”而对“禁人增米价”的政府行为,冯梦龙则讽刺道,“俗吏往往如此。”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赵抃比俗吏的高明之处,是他不迷信政府权力的“看得见的脚”(行政命令),而更相信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正好暗合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
当然,赵抃的赈灾方式能够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也应归功于宋代已经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商品粮市场网络。宋人叶适说,湖南“地之所产米最盛,而中家无储粮。臣尝细察其故矣。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惟意,无有碍隔。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大商则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舰而同营,展转贩粜,以规厚利。”《清明上河图》就画了多条停泊在汴河上的漕船,那都是从南方运粮前来京师的。这些漕船看起来不像是官船(因为不见官兵押运),而是私人船只,可见当时民间市场化的漕运是相当发达的。
二十五年前范仲淹在杭州赈灾时,已经巧妙地运用了“看不见的手”,当时杭州米价升至120文每斗,范仲淹贴出榜文,称以每斗180文收购粮食,“商贾闻之,晨夕争先,惟恐后,且虑后者继来。米既辐凑,价亦随减”。
值得指出的是,并非只有范赵二公有此智慧,而是越来越多的宋人都已发现了“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南宋人董煟在他的《救荒活民书》中便明明白白地提出“不抑价”的赈灾主张:“惟不抑价,非惟舟车辐凑,而上户亦恐后时,争先发廪,米价亦自低矣。”董煟曾经看到,有一些地方,“上司指挥不得妄増米价”,“本欲存恤细民”,却“不知四境之外米价差高”,牙侩暗暗增价收购本地之米,转往他州,导致荒情加剧。好事办出了坏事。
赵忭在越州赈灾,也使用过范仲淹的“凯恩斯政策”,“僦(雇佣)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不管是依靠自由市场的机制来置配赈灾的资源,还是利用凯恩斯手段刺激经济,这一右一左的政策,当时都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想来,不能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附录【李竞恒】《孟子思想与克服“时间偏好”》
作者:李竞恒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文史天地》2023年第3期
奥地利经济学派有一项“时间偏好”(Time preference)的理论,讲现在消费与将来消费的边际替代率,说简单点就是储蓄给将来,还是马上就消费。马上就消费,就是有更强的时间偏好,反之就是时间偏好更低,如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就曾经在内华达大学的课堂上提到同性恋有更高时间偏好,因为没有子嗣作为未来的储蓄。
实际上,人类文明的诞生本身就是克服时间偏好的产物,因为从人的天性来说,都倾向于马上享受得到的事物,而将其进行储蓄留给未来,则需要克服本性,克服那种根深蒂固“爽一把就死”的原始本能。抓住一只小羊,忍住马上就将其吃掉的本能,而是把它养大,未来就能获得稳定的奶和羊毛,而农业和储存粮食更是训练了人克服时间偏好的能力,大量物质的储蓄也让一些人可以脱离农业劳动,产生了复杂的社会分工,进而促进了文明的诞生。
实际上,农业的诞生有效促进了人类克服时间偏好的能力,因为在狩猎采集社会,人们会倾向于将猎物和果实快速食用,而不是用以储蓄。而农业社会,必须克服时间偏好,忍着饥饿也要守着田里的谷物,留下一些储蓄作为来年的种子。如果收成好,就会储蓄更多粮食,最终成为未来的财富。
财产权的稳定,可以有助于人们克服时间偏好,有了稳定财产,一切储蓄都是有意义的,能看到明天的希望,除了积累财产,还包括储蓄善行、为家人积累口碑,这些都是留给未来和子孙的宝贵财富,这样的社会必然有利于美德的培养。反之,在超强时间偏好的社会,因为无法保证有财产或信誉之类,人们会倾向于在短时间内骗一把、抢一把就跑,爽一把就死。很显然,有稳定的共同体、财产能得到保护的地区和人群,可以更好地克服时间偏好,积累美好的未来。而共同体瓦解、遍地原子散沙,或者多天灾人祸的地方,很难积累稳定财产,这些地区和人群就倾向于短时间的博弈,爽一把再说,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
一
《围城》里面有个著名的“葡萄论”,就是先挑最好的葡萄吃,还是把好葡萄留到最后吃。如果从教育小孩克服时间偏好的角度,我会非常鼓励教小孩要把好吃的留到最后再享用,而克服自己首先就吃最好葡萄的那种原始本能。在汉语中,“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饮鸩止渴”这些体现超高时间偏好行为的词语都属于贬义词,这也意味着中国民间主流文化传统还是以克服时间偏好为价值取向的。
汉代民间就有很多存钱罐“扑满”,刘歆《西京杂记》卷五描述说:“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就是说扑满是当时储存硬币的存钱罐,民间普遍习惯储蓄硬币,而不是钱到手就马上花掉,表明至少汉代开始中国民间就有储蓄未来、克服时间偏好的文化,这和汉儒对社会的重建是有关的。
《孟子·滕文公上》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非常清楚,民众的财产得到稳定的保护,成为“恒产”,他们才能拥有“恒心”,即成为克服时间偏好后的文明人。只有在财产得到保护的前提下,自己一切给未来的储蓄——无论是多生几个小孩有助于养老、多收获了几担谷子换成铜钱储蓄、或者在村里帮助别人收获了良好口碑,这些才对自己的未来是有利的。反之,孟子说如果财产得不到保护,民众就会产生超高的时间偏好,即“无恒产者无恒心”,反正无论我怎么积累钱,马上就被石壕吏们榨取走了,我做好事积累口碑,马上被骗子利用还沦为笑话和反面教材,既然如此,那还是做坏事划算,至少偷一把、骗一把搞到钱马上胡吃海喝到肚子里面最实在。所以孟子说,这种超高时间偏好的社会,即“无恒产”和“无恒心”的社会,一定是“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当然,孟子还提出了“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即华夏社会受过绅士教育的精英“士”,无论在任何情形下都要保持克服时间偏好的能力,对积累未来负责任,即使是没有稳定财富,也不能像普通民众一样随波逐流,去骗去偷,而是用尽一切条件和努力去重建社会,让人们重新获得稳定的财产——即孟子所说的“制民之产”,然后去积累和储蓄未来。
要克服时间偏好,稳定的小共同体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熟人社会作恶成本高,俗话讲“兔子不吃窝边草”就是描述这种小共同体内的作恶成本问题。无论是家庭、家族还是跨血缘的乡党、村社这些小共同体,都是世世代代一起生活和博弈的人,因此博弈的时间线非常长,人们会考虑很长远的未来关系等制约条件,因此会克服时间偏好,不会像很多流民陌生人社会那样去作恶,爽一把就跑。孟子主张“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即乡党、村社世代互助的小共同体,内部成员互相扶持一起积累未来。这种关系,不仅仅是村社成员之间,还包括村社的领主,也和治下的村民之间凝结成世代博弈的关系,因此不会像后世那种只当三年就拍屁股走人的流官一样,具有超强时间偏好,赶快搞个大的政治工程然后升官走人,至于留下什么烂摊子不关他的事。王夫之曾这样描述孟子推崇的“三代”时期画面:“名为卿大夫,实则今乡里之豪族而已。世居其土,世勤其畴,世修其陂池,世治其助耕之氓,故官不侵民,民不欺官。”(《读通鉴论》卷十九)王夫之提到这些领主和他们属下的民众之间,是世世代代互相打交道的关系,博弈时间线非常长,作恶成本高,因此领主不欺负属民,属民也不欺负领主,双方都克服了时间偏好,考虑更长远子孙的未来和子孙的关系。
傅斯年也观察到,古老封建时代的官民关系亲密。他说:“试看《国风》,那时人民对于那时公室的兴味何其密切。”(傅斯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自《史学方法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7页)因为双方都属于世代博弈和交道的共同体内,这和后世流官完全不同。在流官的时代,频繁爆发农民起义,因为流官只对朝廷负责,反正当几年官就走人,时间偏好极其强烈,赶快搞个大工程,升迁走人,至于当地以后怎么样,关本官啥事?但封建时代,领主和属民的关系是以动辄几百年来计算的,因此双方的博弈行为模式都是最大化克服时间偏好,会考虑得非常长远。
顾炎武就意识到地方官克服自己时间偏好的重要性,长治久安就是克服时间偏好,有世家的社会,考虑的时间线条就更长,这就是更低的时间偏好。因此他在《郡县论》中提出要让县令世袭的方案,如果县令做得好、不违法,就可以传给子孙,完全和当地人同生死共命运,那么县令的思考时间线就会大不一样,他会尽可能克服时间偏好,为这个县的长远未来,以及自己在这个县的长期名誉、口碑而努力,因为自己家族的未来已经和这个地方永久绑定在一起。所以,顾炎武“寓封建于郡县”的思路,就是鼓励在县一级地方培植扎根深、考虑未来更长远、时间偏好更低的一些世家治理。这恰恰是帮助中央集权郡县制时代,克服时间偏好和彻底掏空地方的一种手段,保护了各个县一级的自治与长远未来。在没有封建的时代,却能得到封建的好处,而避免封建的坏处。
如果理解到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孟子提出“世卿世禄”的思想了,所谓“仕者世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下》),古老封建时代的官职长期是由一些家族世代担任的,西周铜器铭文经常会有周王任命新一代官员“更乃祖司某事”,即继承家族的世代职业和手艺。由于会考虑家族世世代代职业的口碑,这些世官会特别讲究类似工匠精神的东西,如以史官为例,封建时代的史官特别讲究秉笔直书这种职业道德,很大程度上就是史官整个家族和这一职业道德的绑定。王安石在《答韶州张殿臣书》中说:“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当时很多史官如董狐或者齐国的北史氏、南史氏之类,都是不避刀斧,也要坚持秉笔直书的,这是封建时代世卿世禄制度下,一个时代职业家族的职业伦理,这种世卿会考虑整个家族长远的利益和口碑积累,克服时间偏好,他们考虑的家族博弈时间线,动辄是以几百年为单位的,很长远,哪怕暂时吃亏,家中有人因秉笔直书被杀,但长远看却进一步积累了家族的良好口碑,对于未来更加有利。所以,孟子主张的世卿世禄背后,也有克服时间偏好的这一面。
二
与这些稳定长远共同体形成对比的,就是流民散沙社会,陌生人之间博弈线条极短,因此往往具有超强时间偏好,倾向于爽一把就死。
东晋时期的成汉君主李寿,在咸康四年(338)就曾经有一次占卜,得到结论是可以当几年皇帝。他手下的罗恒、解思明等都劝他不要自称皇帝,而是称成都王、益州牧就行了,以诸侯身份向东晋称臣,就可以得到东晋的保护,从而长远地当诸侯,延续自己的家族。所谓“数年天子,孰与百世诸侯”,当几年皇帝,哪有当上百代诸侯好?但是李寿生自流民家族,有强烈的时间偏好,他竟然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是爽一把皇帝就行(《资治通鉴·晋纪十八》)。既然称皇帝,那就是摆明和东晋作对,后来成汉被桓温所灭,也是咎由自取。显然,李寿完全误读了孔子那句话,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是“道”如果可以实现,自己愿意死去(李竞恒:《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8页),而“道”的实现恰恰是遍地都是克服时间偏好的自治共同体,而不是超强时间偏好的流民散沙。与李寿相比,同是东晋南朝的琅琊王氏,就非常聪明,晋、宋、齐、梁、陈朝代不断变化,但琅琊王氏的地位却不变,以“百世诸侯”的身份延续了三百年的基业,而不是灿烂几年就灭亡。显然,贵族精神品质的士族,比流民更能克服自己的时间偏好。
到了宋代,随着中古时期贵族社会的瓦解,出现了更均质性和扁平的社会结构,在“齐民”之间身份更平等的同时,问题也随之出现,就是更平民化的家庭组织不像古代贵族家族那样,能更好地克服时间偏好。对此宋儒张载有一番论述:“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张载集·经学理窟》,中华书局,2019年,第259页)。张载认为,孟子推崇的世家、世臣是一个社会和国家的顶梁柱和凝结核,贵族世家的时间考虑范围非常长远,如周公动辄“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琅琊王导动辄卜得“淮水竭,王氏灭”,家族生命线与大自然河流的生命一样久远。如果和这些贵族世家动辄几百上千年的时间线相比,来自平民科考当官的家庭,时间偏好确实更强烈,只是倾向于考虑“三四十年之计”,哪怕当了一回宰相,也不过造一栋大豪宅,然后死掉,家产就被子女们分了,散沙化、原子化,如同一个美丽烟花,绚烂绽放瞬间,然后烟消云散,什么都留不下。
因此,张载主张平民精英模仿先秦贵族,建立宗法,通过宗法手段建立起模仿古代贵族家族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通过宗法手段获得长远的生命,尽量不散沙化,而是将散沙的核心小家庭团成宗族共同体。个体的生命有限,但宗法承载的生命河流共同体可以无限,这样就不会只是考虑“三四十年之计”,而是会动辄考虑几百年、上千年的未来,那么博弈的行为模式就一定会很稳健,不会轻易干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和不考虑长远未来和子孙的事。宋代范仲淹留下的范氏义庄,运转九百年,堪称平民社会模仿古代贵族世家最成功的例子之一,这种动辄九百年的世家一定会强有力地克服时间偏好,而如果遍地都是这样的世家,对于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附录【李竞恒】《孟子论克服时间偏好:稳定的共同体、恒产是文明的前提》
作者:李竞恒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南方周末》2022年6月30日
奥地利经济学派有一项“时间偏好”(Time preference)的理论,讲现在消费与将来消费的边际替代率,说简单点就是储蓄给将来,还是马上就消费。
实际上,人类文明的诞生本身就是克服时间偏好的产物。因为从人的天性来说,都倾向于马上享受得到的事物,而将其进行储蓄留给未来,则需要克服本性,克服那种根深蒂固“爽一把就死”的原始本能。抓住一只小羊,忍住马上就将其吃掉的本能,而是把它养大,未来就能获得稳定的奶和羊毛,而农业和储存粮食更是训练了人克服时间偏好的能力,大量物资的储蓄也让一些人可以脱离农业劳动,产生了复杂的社会分工,进而促进了文明的诞生。
财产权的稳定,可以有助于人们克服时间偏好,有了稳定财产,一切储蓄都是有意义的,除了积累财产,还包括储蓄善行、为家人积累口碑,这些都是留给未来和子孙的宝贵财富,这样的社会必然有利于美德。反之,在超强时间偏好的社会,因为无法保证有财产或信誉之类,人们会倾向于在短时间内骗一把、抢一把就跑、爽一把就死。
很显然,有稳定的共同体、财产能得到保护的地区和人群,可以更好地克服时间偏好,积累美好的未来。而共同体瓦解、遍地原子散沙,或者多天灾人祸的地方,很难积累稳定财产,这些地区和人群就倾向于短时间的博弈,爽一把再说,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围城》里面有个著名的“葡萄论”,就是先挑最好的葡萄吃,还是把好葡萄留到最后吃。
《孟子·滕文公上》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非常清楚,民众的财产得到稳定的保护,成为“恒产”,他们才能拥有“恒心”,即成为克服时间偏好后的文明人。只有在财产得到保护的前提下,自己一切给未来的储蓄——无论是多生几个小孩有助于养老、多收获了几担谷子换成铜钱储蓄,或者在村里帮助别人收获了良好口碑,这些才对自己的未来是有利的。
反之,孟子说如果财产得不到保护,民众就会产生超高的时间偏好,反正无论我怎么积累钱,马上就被石壕吏榨取走了,我做好事积累口碑,马上被骗子利用还沦为笑话和反面教材,既然如此,那还是做坏事划算,至少偷一把、骗一把搞到钱马上胡吃海喝到肚子里面最实在。所以孟子说,这种超高时间偏好的社会,一定是“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
当然,孟子还提出了“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即华夏社会受过绅士教育的精英“士”,无论在任何情形下都要保持克服时间偏好的能力,对积累未来负责任,即使是没有稳定财富,也不能像普通民众一样随波逐流,去骗去偷,而是用尽一切条件和努力去重建社会,让人们重新获得稳定的财产,即孟子所说的“制民之产”,然后去积累和储蓄未来。
要克服时间偏好,稳定的小共同体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熟人社会作恶成本高,俗话讲“兔子不吃窝边草”就是描述这种小共同体内的作恶成本问题。无论是家庭、家族还是跨血缘的乡党、村社这些小共同体,都是世世代代一起生活和博弈的人,因此博弈的时间线非常长,人们会考虑很长远的未来关系等制约条件,因此会克服时间偏好,不会像很多流民陌生人社会那样去作恶,爽一把就跑。孟子主张“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即乡党、村社世代互助的小共同体,内部成员互相扶持一起积累未来。这种关系,不仅仅是村社成员之间,还包括村社的领主,也和治下的村民之间凝结成世代博弈的关系。
王夫之曾这样描述孟子推崇的“三代”时期画面:“名为卿大夫,实则今乡里之豪族而已。世居其土,世勤其畴,世修其陂池,世治其助耕之氓,故官不侵民,民不欺官”(《读通鉴论》卷十九),王夫之提到,这些领主和他们属下的民众之间,是世世代代互相打交道的关系,博弈时间线非常长,作恶成本高,因此领主不欺负属民,属民也不欺负领主,双方都克服了时间偏好,考虑更长远子孙的未来和子孙的关系。
如果理解到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孟子提出“世卿世禄”的思想了,所谓“仕者世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古老封建时代的官职长期是由一些家族世代担任的,西周铜器铭文经常会有周王任命新一代官员“更乃祖司某事”,即继承家族的世代职业和手艺。由于会考虑家族世世代代职业的口碑,这些世官会特别讲究类似工匠精神的东西,如史官为例,封建时代的史官特别讲究秉笔直书这种职业道德,很大程度上就是史官整个家族和这一职业道德的绑定。王安石在《答韶州张殿臣书》中说“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当时很多史官如董狐,或者齐国的北史氏、南史氏之类,都是不避刀斧,也要坚持秉笔直书的,这是封建时代世卿世禄制度下,一个时代职业家族的职业伦理,这种世卿会考虑整个家族长远的利益和口碑积累,克服时间偏好,哪怕暂时吃亏,家中有人因秉笔直书被杀,但长远看却进一步积累了家族的良好口碑,对于未来更加有利。所以,孟子主张的世卿世禄背后,也有克服时间偏好的这一面。
(作者系大学教师、历史学者)
第5章 生而平等
“平等“”自由”——《独立宣言》中的这两个词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它们所表达的理想能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平等与自由是相互一致的,还是相互抵触的?
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早在《独立宣言》之前,就已对美国历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寻求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形成了知识界的舆论,导致了血腥的战争,造成了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的巨大改变。寻求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将继续是我们政治辩论的主要内容。它将象影响我们的过去一样,影响我们的未来。
在共和国建国伊始的年代,平等指的是在陡斯面前的平等;自由指的是决定个人命运的自由。《独立宣言》和奴隶制之间明显的冲突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南北战争最后解决了这场冲突。辩论于是转到另一个高度。平等越来越被解释为“机会均等”,即每个人应该凭自己的能力追求自己的目标,谁也不应受到专制障碍的阻挠。对于大多数美国公民来说这仍然是平等的主要含义。
无论是陡斯面前的平等还是机会均等,都同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不存在任何冲突。恰恰相反,平等和自由是同一个基本价值概念——即应该把每个人看作是目的本身——的两个方面。
最近几十年来,平等这个词在美国开始具有一种同上述两种解释很不相同的含义,即结果均等。每个人应享有同等水平的生活或收入,而且应该结束竞争。结果均等显然是与自由相抵触的。努力推进这种均等,是造成政府越来越大并使我们的自由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
陡斯面前的平等
当托马斯·杰斐逊在三十三岁上写下《人人生而平等》时,他和他的同时代的人们并没有就字面上的含义来理解这些词。他们并不认为“人”——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个人”——在身体特征、情绪反应、技艺和知识上是平等的。托马斯·杰斐逊本人就是出类拔萃的人。在二十六岁那年,他设计了坐落在蒙提塞洛(意大利语意为“小山”)的漂亮房子,亲自监督建造,据说还自己动手。在他的一生中,他曾经是发明家、学者、作家、政治家、弗吉尼亚州州长、美国总统、驻法国大使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人——总之,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普通的人。
杰斐逊和他的同时代的人们对平等的理解,可以从《独立宣言》的下一段话中看出:“造物主赋予人们以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耶和华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其自己的价值。他有不可转让的权利,任何人不能侵犯。他有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应简单地被当作达到他人目的的工具。“自由”是平等定义的一部分。并不与平等相冲突。
耶和华面前的平等——人身平等——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人不是个个一样的。他们的不同价值观、不同爱好、不同能力使他们想过很不相同的生活。人身平等要求尊重他们这样做的权利,而不是强迫他们接受他人的价值观或判断。杰斐逊毫不怀疑,某些人优于另一些人,也不怀疑杰出人物的存在。但这并不赋予他们统治别人的权利。
如果说杰出人物集团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那么,任何其他集团,即便在人口中占大多数,也不拥有这种权利。每个人应该是他自己的统治者,只要他不去干涉别人同样的权利。建立政府是为了保护这种权利,使其不受其它公民或外界的威胁,而不是让多数人毫无约束地统治其他人。
杰斐逊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他生前取得的三项成就:一、在他任州长时,弗吉尼亚州通过了宗教自由法(该法是旨在保护少数人不受多数人统治的“美国权利法案”的前身),二、起草《独立宣言》,三、创办弗吉尼亚大学。由杰斐逊的同时代人起草的美国宪法,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全国性政府,以保卫国家,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但同时要严格限制它的权力,以保护每一个公民和各州政府不受全国政府的支配。统治民主,是指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府活动,显然不是指政治上由多数人实行统治。
著名的法国政治哲学家和社会学家A.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对美国作了长期访问后,写了一本不朽的著作,名叫《美国的民主》。他在书中认为美国的突出特征是平等,而不是多数人统治。他写道:
“在美国,贵族政治因素从一开始就是微弱的。即使它们尚未被完全肃清,它们现在也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很难再对事态产生任何影响。相反,民主原则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以及各项法律的制定而得到极大的加强,该原则不仅压倒了其他一切原则,而且成了无所不能的灵丹妙药。在美国,没有哪个家族或公司能够发号施令。……
因而,美国社会展示了最为奇特的现象。那里的人们看上去在财富和智力上,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力量上,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或任何有文字可考的古人,都享有更大的平等。”
托克维尔对他的所见所闻大加赞美,但他并不是盲目的吹捧者,他担心民主搞得过火,会败坏人们的德行。他写道:“有……一种大丈夫气概的合法的要求平等的热情,激励人们追求权力和荣誉。这种热情会把卑微者提升到伟大人物的行列;但是,在人类的心灵中也有一种对平等的卑劣憎恶,它驱使弱者将强者降低到与他们相同的水平,使人们宁可要奴隶制下的平等,也不要自由下的不平等。”
最近几十年中,美国民主党成了加强政府权力的首要工具,而在杰斐逊和许多他的同时代人的眼中,政府权力是对民主的最大威胁。这是字义变化的惊人证据。民主党是以促进“平等”的名义增加政府的权力的,而这种“平等”的概念,同杰斐逊认为与自由等同和托克维尔认为与民主等同的平等的概念,几乎截然相反。
当然,开国元勋的实践并不总是符合他们所宣扬的理论。最明显的言行不一,表现在奴 隶制问题上。托马斯·杰斐逊直到他死的那一天,即1826年7月4日,还拥有奴隶。他生前一再表示对奴隶制痛心疾首,他在笔记和通信中,都提过消灭奴隶制的计划,但他从未公开提出任何这种计划,也没有在竞选中反对过奴隶制。
然而,如果不废除奴隶制,他苦心建立的国家就将公然违背他所起草的《独立宣言》。因而毫不奇怪,在共和国最初的几十年中,关于奴隶制的论战越来越凶。这场论战的结果是一场内战。正如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讲演中所说,内战考验了“一个在自由中诞生的、以人生而平等为宗旨的……国家,能否长期坚持下去。”
这个国家坚持下来了。然而,是以无数生命、财产的损失和社会动乱为代价坚持下来的。
机会均等
内战一旦废除了奴隶制,人身平等——在耶和华和法律面前平等——接近于实现后,知识界讨论的重点和政府与私人政策的重点,就转到另一个概念,即机会均等上来了。
实实在在的机会均等——即所谓“同等”——是不可能的。一个孩子天生就是瞎子,而另一个则视力完好;一个孩子的父母从小就对他的幸福特别关心,提供良好的文化学习和智力发展的条件,而另一个孩子的父母则生活放荡,对孩子放任不管;一个孩子出生在美国,而另一个出生在印度、中国或苏联。显然,他们并不是生下来就享有同等的机会。而且,也无法使他们的机会同等。
同人身平等一样,机会平等也不能完全按字面来理解。它的真正含义的最好的表达也许是法国大革命时的一句话:前程为人才开放。任何专制障碍都无法阻止人们达到与其才能相称的、而且其品质引导他们去谋求的地位。出身、民族、肤色、信仰、性别或任何其他无关的特性都不决定对一个人开放的机会,只有他的才能决定他所得到的机会。
按照这种解释,机会均等只不过是更具体地说明人身平等和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含义。与人身平等一样,机会均等之有意义和重要,正是因为人们的出生和文化素质是不同的,因此,他们都希望并能够从事不同的事业。
同人身平等一样,机会均等与自由并不抵触。相反它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有些人仅仅因为某个种族出身、肤色或信仰而受到阻挠,得不到他们在生活中与他们相称的特定地位的话,这就是对他们的“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干涉。这就否定机会均等,也就是为一些人的利益牺牲另一些人的自由。
象每一种理想一样,机会均等很难完全得到实现。毫无疑问,对这一原则的最严重的背离是在黑人问题上,特别是在南方,但在北方也不例外。然而,在为黑人和其他集团取得机会均等方面,也有巨大的进步。“大熔炉”的概念正是反映了机会均等的目标。另外,大、中、小学“免费”教育的扩大,也反映了这一目标,尽管这种扩大,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并不纯粹是好事。
内战后,在公众普遍接受的价值等级中,机会均等居于优先地位,这特别表现在经济政策上。当时流行的字眼是自由企业、竞争和自由放任主义。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做任何生意,从事任何职业,购买任何财产,只需得到交易对手的同意。干得成功,他就有发迹的机会。但如果失败,就要自食其果。那时没有任何专制障碍。成败的关键是个人的才能,而不是出身、信仰或民族。
一个必然的结果是:被许多自认为是学者名流的人斥之为庸俗唯物主义的东西获得了发展。庸俗唯物主义强调金元万能,以财富为成功的标志。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这种强调反映了人们不愿意接受传统的看重出身和门第的封建贵族社会的标准。着重点明显地换成个人的才能,而财富的积累则是衡量才能的最方便的尺度。
另一个必然的结果自然是人的能力获得了巨大解放,它使美国成为生产率日益提高、越来越生气勃勃的社会。在这里,社会的流动成为日常的现实。还有一个可能令人吃惊的必然结果,就是慈善事业蓬勃兴起。这同财富的迅速增长是分不开的。在当时占优势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下,特别是由于对机会均等的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采取了以下特有的形式:如非营利的医院、私人资助的院校以及旨在帮助穷人的各种慈善机关。
【按:北宋中期及晚明时期的中国也是如此。】
当然,在经济领域同在其他领域一样,现实同理想并非总是一致的。当时政府的作用被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对企业没有设置严重障碍。到十九世纪末,政府采取积极措施,特别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来消灭竞争中的私人障碍。但是,一些不受法律约束的传统,继续妨碍着人们进入某些行业或从事某些职业的自由,而且毫无疑问,社会传统使那些出生在“正统”家庭、生来就有“正统”肤色,而且信奉“正统”宗教的人享有特别有利的条件。然而,各种不那么有特权的人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迅速提高表明,这类障碍决不是不可逾越的。
就政府的措施而言,对自由市场的主要背离在对外贸易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把为保护本国工业而征收关税看作是美国方式的一部分。关税保护同彻底的机会均等(见第二章)是不一致的,而且与自由移民也是不一致的。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除东方人外,世界各地的人均可自由移居美国。然而,人们可以为这种背离寻找国防需要方面的理由,也可以提出另一个性质很不相同的理由,即平等只限于国内。这后一种理由是不合逻辑的,但今天却被大多数鼓吹另一种平等的人所采用。
结果均等
那另一种平等即结果均等,是在本世纪深入人心的。它首先影响了英国政府的政策,继而影响到欧洲大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它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某些知识分子中,结果均等成了宗教信条:大家应当同时停止竞赛。正象《艾丽丝漫游记》中的渡渡所说:“人人获胜,都该得奖。”
这一概念同另外两种概念一样,“均等”也不能按字面解释为“等同”。其实,谁也不主张不问年龄、性别或身体素质,人人都分得同样份额的食品或衣服等等。虽然所要达到的目标相当“公平”,但“公平”却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一个确确实实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给以精确定义的概念。“对所有人公平分配”是取代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新口号。
结果均等的概念与前两个概念有着天壤之别。促进人身平等或机会均等的政府措施增大自由;致力于“对所有人公平分配”的政府措施减少自由。如果人民的所得依“公平”来定,又由谁来决定什么是“公平的”呢?就象大家同声问渡渡的:“可是谁来发奖呢?“”公平”一旦离开比较的对象,就不成为客观决定的概念了。“公平”如同“需要”一样,全在怎么看。如果所有人都要“公平份额”的话,那就必须由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来决定什么样的分配是公平的,而且他们必须能够把他们的决定强加给别人,从财产多于“公平”份额的人那里拿走一部分,给予财产少于“公平”份额的人。那些作决定并强加于人的人与听从他们决定的人能是平等的吗?我们不就进了乔治·奥韦尔的《动物饲养场》了吗?在那里,“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另外,如果人们的所得是靠“公平”而不靠他们所生产的东西来决定,“奖品”又从哪里来呢?还能有什么刺激人们去工作和生产呢?怎样决定谁来当医生,谁当律师,谁捡垃圾,谁扫街呢?由什么来保证人们接受分配给他们的任务,并按他们的能力来完成呢?显然,只有靠强力或强力威胁。
这里的关键不光是实践会同理想分离。同另外两种有关平等的概念一样,它们当然是要分离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公平分配”或其前身“按需分配”的理想与人身自由的理想之间有着根本的冲突。在人们试图使结果均等成为社会组织的最高原则的所有尝试中,都存在着这种冲突。其无法避免的最终结果是恐怖国家的出现:苏联、中国以及新近的柬埔寨可以说是清楚而令人信服的例证。而且,即便采取恐怖手段,也不曾使结果均等。在上述的每个国家中,无论拿什么标准来衡量,都存在着广泛的不平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仅在权力上,而且在物质生活上都不平等。
西方国家在促进结果均等的名义下采取的远不那么极端的措施,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只是程度稍轻罢了。它们也限制个人的自由,但它们同样没有达到其目标。这说明要把“公平份额”按普遍能接受的方式规定下来,或使社会成员对所受到的“公平”待遇感到满意,是不可能的。相反,越是试图扩大结果均等,越会激起人们的不满情绪。
推动结果均等的道德热情,大部分来自一种普遍的信念,即认为一些孩子仅仅因碰巧父母有钱就比其他孩子优越是不公平的。这当然是不公平的。然而,不公平可采取多种形式。它可以采取财产继承形式,如继承债券、股票、房产和工厂,也可采取天资继承的形式,如继承音乐才能、体力、数学天才等。财产继承比天资继承更容易遭到干涉。但从伦理的角度来看,这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呢?然而,许多人对财产继承感到愤恨,而对天资继承却不在乎。
现在,让我们从做父母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想使你的孩子一生中有较高的收入,那你可以采取各种方法做到这一点。你可以花钱让他(她)受教育,使他(她)有条件从事高收入的工作;或者,你可以为他开个店,使他能得到高于受雇人员的收入;你还可以给他留下一笔财产,让他靠财产收入过富裕日子。从伦理上看,这三种运用财产的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呢?再说,如果国家在课税后给你剩下任何钱的活,难道国家只允许你拿它过放荡的生活,而不准你把钱留给你的孩子吗?
这里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是微妙而复杂的,不能用“对所有人公平分配”那种简单化的公式来解决。因为,假如我们当真那么做的话,我们就得给予音乐才能差的青年最大量的音乐训练,以弥补他们天分之不足;而对那些音乐天分高的青年,却要剥夺他们受到良好音乐训练的机会;在个人天资继承的其他方面,也是一样。这样做对于天资差的青年可能是“公平”的,但对于天资好的青年,这是否“公平”呢?更不必说那些不得不为支付训练天资差的青年而工作的人,或者那些本可以从培养有才华者得到好处却因此得不到的人们了。
生活就是不公平的。相信政府可以纠正自然产生的东西是诱人的。但是,认识到我们正是从我们所哀叹的不公平中得到了多少好处,也同样是重要的。
马琳·迪特里希天生一对诱人而美丽的大腿,穆罕默德·阿里天生就有使他成为拳王的本事,这没有什么公平可言。但就另一方面讲,千百万喜欢看马琳·迪特里希的大腿或阿里的拳赛的人,却从自然界不公平地产生了迪特里希和阿里这件事中得到了好处。如果世界上的人都是一个样,这个世界还成什么世界呢?
穆罕默德·阿里一晚上能挣数百万美元,这肯定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为了追求某些抽象的平等理想,不允许阿里一个晚上的拳击(或每天为这场拳击进行的准备)的所得,比一个最底层的人在码头上干一天粗活挣得多的话,这对于那些喜欢看他比赛的人来说,岂不是更不公平吗?就算能够这样做,但其结果将是剥夺人们欣赏阿里拳技的机会。如果把给阿里的报酬限于码头工人一样的水平,我们很怀疑阿里还会忍受赛前的艰苦训练,并投身他经历过的那种搏斗。
公平这一复杂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可以通过赌牌这类碰机会的玩意儿来说明。晚上纸牌开局的时候,各个赌家的筹码的数量是相等的。但玩了一段时间后,数量就会不相等了。当晚收局时,某些人成了大赢家,另一些人成了大输家。按照平等的理想,是不是赢家得把赢的钱还给输家呢,如果真是这样,游戏就会变得毫无趣味,连输家也会觉得没意思。他们也许会玩上一两次,但如果他们知道,不论输赢,收局时还会同开局时一样的话,他们还会再玩吗?
这一例子同现实世界的关系,可能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大得多。每天,我们各自都要做出一些决定,碰碰机会。有时是大的机会,如决定从事什么职业,与谁结婚,买房子还是作一笔大的投资。更经常的是一些小的机会,如决定去看什么电影,在不在交通拥挤的情况下横穿马路,买这种保险还是那种保险。每次的问题在于由谁来决定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这个问题又取决于谁承担这些决定的后果。如果是我们承担后果的话,我们就可以作决定。但如果是别人承担后果的话,那么,该由我们或者能够由我们来做决定吗?如果你用另外一个人的钱,替他打牌的话,他会允许你自由作出决定吗?他不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你作出决定的权力,而且定下一些规矩让你遵守吗?再举一个全然不同的例子:如果政府(即你的纳税伙伴们)负责补偿洪水给你的房屋造成的损失,那还能够由你自由决定把房子再建到洪水淹了的平原上吗?政府对个人决定的干涉随着“对所有人公平分配”的运动的开展而不断增加,这并非是偶然的。
人民自己作出抉择并承担这些决定的大部分后果,这是贯穿着我国大部分历史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在过去二百年间刺激了福特家族、爱迪生家族、伊斯特曼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彭尼家族去改造我们的社会。正是这种制度刺激了另一些人,使他们乐意担风险、掏钱来资助这些野心勃勃的发明家们和产业大亨们从事冒险事业。当然,一路上有许多失败者,失败者也许比成功者要多。他们的名字被人遗忘了。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是甘愿冒风险的。他们知道自己是在碰机会。而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整个社会由于他们愿意碰这个机会而得到了好处。
这个制度所生产的财富主要来自发展新的产品或服务,来自生产这些产品或服务的新方法,也来自广泛分配这些产品或服务的新方法。由此给整个社会增加的财富和给人民群众增加的福利,要比这些创业者积累的财富多许多倍。亨利·福特发了大财,而国家得到了一种廉价而可靠的运输工具和成批生产的技术。另外,个人财富最后大部分还是用在社会福利上。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只是无数私人慈善活动中最为著名的。这些私人慈善事业是一个符合“机会均等”和“自由”的制度运行的突出结果。这里的“机会均等”和“自由”,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意义上的均等和自由。
我们只需要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海伦·霍罗威兹在一本论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1907年芝加哥文化慈善事业”的书中写道:
“在上世纪初和本世纪末,芝加哥是个被各种相互对立的力量推动的城市:它一方面是一个经营工业社会生产的基本商品的商业中心;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文化事业蒸蒸日上的地方。正如一位评论家说的,这个城市是‘一个猪肉和柏拉图的奇怪的混合体。’
“芝加哥文化运动的主要表现,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建立起了该城的一些伟大的文化机构,如艺术研究所、纽伯里图书馆、芝加哥交响乐团、芝加哥大学、费尔德博物馆、克里勒图书馆。……
“这些机构是该城市的新气象。无论最初建立时的动机是什么,它们大部分是由一伙工商业者所组织、维持和控制的。……尽管是由私人支持和管理,这些机构却都是为整个城市设计的。它们的托管人转向文化慈善事业,主要不是为满足个人对艺术或学术的向往,而是为了达到社会的目的。这些工商业者受到他们无法驾驭的社会势力的困扰,满怀文化的理想主义情绪,把博物馆、图书馆、交响乐团和大学看作是净化城市和发动城市(文艺复兴)的手段。”
慈善事业绝不仅仅限于文化机构。正如霍罗威兹在另一处写道的,这是“一种在许多不同方面爆发的活动”。芝加哥并不是孤立的例子。用霍罗威兹的话来说,“芝加哥似乎是美国的缩影”。正是在这一时期,在简·亚当斯的倡导下,芝加哥建立了赫尔贫民习艺所。赫尔贫民习艺所是在全国建立的许多贫民习艺所中的头一个。这些贫民习艺所是用来在穷人中传播文化和教育,并帮助他们解决日常问题的。另外,在这期间还建立了许多医院、孤儿院和其他慈善机构。
在自由市场制度与追求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目标之间,或在自由市场制度与对不那么幸运者的同情之间没有相抵触的地方,不管这种同情采取十九世纪私人慈善活动的形式还是采取二十世纪越来越多的通过政府来援助的形式——只要它们都反映一种帮助他人的愿望。由政府援助穷人的两种形式表面看上去相似,其实有天渊之别:第一种形式是,我们90%的人都赞同自己纳税来帮助处于底层的10%的人。第二种形式是,80%的人投票赞成让处于最上层的10%的人纳税来帮助处于最底层的10%的人。这就是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关于由B和C来决定D应为A做些什么的著名事例。第一种形式可能是明智的,也可能是不明智的;可能是帮助不幸者的有效率的方法,也可能是缺乏效率的方法。但是,它与机会均等和自由的信仰是一致的。第二种形式追求结果均等,与自由是完全对立的。
哪些人赞成结果均等?
支持结果均等这个目标的人寥寥无几,尽管在知识分子中,它简直成了宗教信条,在政治家的演说和各项法律的序言中被大肆宣扬。政府、最狂热信奉平等的知识分子们以及一般大众的所作所为,都使这种关于结果均等的谈论变成空话。
【按:文化马克思主义是马教版本的“新教”或“逊尼派”。】
拿政府来说,一个明显的事例是对彩票和赌博的政策。人们普遍而且正确地认为,纽约州特别是纽约市,是平等情绪的堡垒。然而,纽约州政府就经营彩票,并为赛马中的赌博提供方便。为引诱市民购买彩票和在赛马中打赌,它大作广告,以便为政府捞得巨额利润。同时,它尽力压制“数字彩票”赌博,因为“数字彩票”赌博比政府彩票更有赢头(特别是考虑到赢家容易逃税)。英国即使不是平等思想的发源地,也是平等思想的堡垒,但它却允许开设私人赌场,允许在赛马和其他体育项目中进行赌博。赌博确实成了一种全国性的娱乐活动和政府收入的一大来源。
拿知识分子来说,最清楚的证明是他们未能把他们那么多人宣扬的事付诸实践。可以由他们自己亲自试一试怎样实行结果均等。首先得确定所谓均等指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在美国国内实行,还是在整整一批选定的国家内实行,还是在整个世界实行?以哪种收入作标准?个人的?家庭的?一年的?十年的?还是一生的?是单指货币形式的收入呢?还是也包括下面这样一些非货币的项目,如自有自住的房屋、自种自食的粮食、家庭成员尤其是家庭主妇的非花钱雇用的服务?身体和智力的优劣又怎么算?
无论你如何断定这些问题,只要你是平等主义者,就可以估计出什么样的货币收入符合你的平等概念。如果你的实际收入高于这个标准,你可以留下标准内的部分,把多余的部分分给收入低于这一标准的人。如果你的标准要包括全世界,象大多数平等主义言论所主张的那样,那么,每人的年平均收入将低于二百美元(以1979年美元价值计算),这个数量将是符合大多数平等主义言论所讲的平等概念的。这大约是全世界平均每人的收入。
欧文·克里斯托尔的所谓“新阶级”:即政府官僚、由政府基金资助进行研究或由政府资助的“智囊团”雇用的学者、许多所谓“总体利益”或“公共政策”集团的成员、记者和从事新闻事业的其他人员,都是平等学说最热烈的鼓吹者。然而,他们使我们想起了关于公馆会教士们的一个古老的(如果是不公正的话)谚语:“他们到新世界来行好,结果自己过得挺好。”新阶级的成员总的来说属于社会上挣钱最多的人,而且,对于其中许多人来说,宣扬平等,设法通过并实施这方面的法律,已证明是得到这种高收入的有效手段。我们大家都容易把自己的福利等同于社会福利。
当然,平等主义者可能会提出抗议,说他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如果别人都被迫那样做的话,他将乐意拿出他认为超过平等水平的那部分收入来重新分配。一方面,认为强制手段将改变事态的看法是错误的——即使其他人都这样做,他对别人收入的贡献也仍将只是沧海一粟。不论他是唯一的捐献者还是许多捐献者中的一个,他个人的贡献总是那么大。的确,他可以把他捐的钱直接给予那些他认为是合适的接受者中最贫穷的人,从而使他的捐献成为更有价值的事。另一方面,强制手段将使事态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这类再分配行动是自愿的话。将要出现的社会将同强迫人们进行再分配而出现的那种社会截然不同。按照我们的标准,前一种社会比后一种社会好千百倍。
如果有人认为实行强制性平等的社会更可取,那他们可以亲身实践一下。他们可以加入我国或其它国家的许多现有的公社,也可以建立新的公社。而且,任何一批希望这样生活的人能够自由地这样做,当然是完全符合人身平等、机会均等和自由等信念的。我们的论点,即对结果均等的支持不过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从希望参加那种公社的人数之少,和那些已经建立的公社之脆弱,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美国的平等主义者可能会反驳说,公社的数量少和脆弱是一个“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对它们进行污蔑和因此而使它们受到歧视的结果。这在美国可能是真的,但是,正如罗伯特·诺吉克所指出的,在有一个国家这不是真的,那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在那里,恰恰相反,平等主义公社受到高度重视和赞赏。在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定居的早期,集体农庄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继续在以色列国中发挥重要作用。以色列国领导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成员非但不会受到非议,反而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人们的欢迎。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加入或离开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是有活力的社会组织。然而,不论在任何时候,肯定也包括今天,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人从未超过以色列犹太人口的5%。我们可以把5%这一比例看作是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最多人数,这部分人自愿选择一种强制实行结果均等的制度,而不愿要不平等的、多样性的和有机会的制度。
公众对于累进所得税的态度各不相同。最近,在一些还没采用累进所得税的州曾就征收这种税进行了公民投票,在另外一些州则就提高累进率进行了公民投票,结果一般都被否决了。另一方面,联邦所得税的累进率则很大,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尽管它也包含许多实际上可以大大降低累进率的条款(即“漏洞”)。这表明,公众对于重新分配适当数量的税收还是能够容忍的。
但是,我们要冒昧地说一句,人们对雷诺、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的喜爱,也同样真实地反映了公众的偏好,其真实程度丝毫不亚于联邦所得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社论以及《纽约书评》所反映的情况。
平等政策的后果
我们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我们与它们具有共同的知识和文 化背景,我们的许多价值概念都来源于它们。英国可能是最有启发性的例子。它在十九世纪实行机会均等方面以及在二十世纪实行结果均等方面,都起了表率作用。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的国内政策,一直为寻求更广泛的结果均等所左右。政府采取了一项又一项措施,旨在从富人手里拿走一些财富,分配给究人。所得税率不断提高,最后提高到占不动产收入的98%和“所挣”收入的83%,而且遗产税也越来越重。在向失业者和老年人提供救济的同时,国家还大规模地增加了医疗、住房和其他福利事业。不幸的是,其结果与那些对几世纪来一直占优势的阶级结构十分恼火的人所希望的大不相同。虽然财富被广泛地重新分配,但到头来分配还是不公平。
实际上只是产生了新的特权阶级来代替或补充原有的特权阶级。新的特权阶级包括:握有铁饭碗的官僚们,不论在职期间还是退休之后,他们都受到保护,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工会头头们,即劳工运动的贵族,他们自称为最受压迫的工人讲话,但实际上他们却是这块土地上收入最高的工人;还有新的百万富翁们,他们善于规避从国会和官僚机构中倾泻出来的法律和规章,他们想方设法地逃税漏税;并把财产转移到收税官力所不及的海外去。如果说这是收入和财富的巨大改组,那倒是真的;但如果说这是更大的平等,却不大象。
平等运动在英国失败,并不是由于采取了错误的方法,尽管某些方法的确是错误的;不是由于管理不善,尽管某些方面的管理的确很糟;也不是由于管理人员无能,尽管某些管理人员的能力的确很差。平等运动的失败有其更为根本的原因。它违背了人类的一个最基本的天性,即亚当·斯密所说的,“每个人都为改善自身的境况而作一贯的、经常的和不间断的努力。”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人们也为改善其子孙后代的境况而努力。当然,斯密所说的“境况”不单指物质福利,尽管物质福利肯定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所想的是更为广阔的概念,这一概念包括了所有人用来判断自己成就的价值标准,特别是那种在十九世纪曾促使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社会价值标准。
当法律妨碍人民去追求自己的价值时,他们就会想办法绕道走。他们将规避法律,违反法律,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道德规范,认为强迫人们为他们不赞成的目的交出自己创造的许多东西去帮助不认识的人是合理的。当法律同大多数人认为是合乎道德的而且正当的准则发生矛盾时,他们就会违反法律,不论这种法律是在促进平等这样高尚的理想的名义下通过的,还是赤裸裸地为一个集团的利益而牺牲其他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守法,只是出于害怕受到惩罚,而不是出于正义感和道德观念。
当人们开始违反某一类法律时,不守法的情况就会不可避免地波及所有的法律,甚至影响到那些公认为是合乎道德的和正当的法律,如反对暴力、盗窃和破坏行为的法律。说来也许难以置信,近几十年中,英国有增无减的犯罪活动,很可能正是平等运动的后果。
另外,平等运动把一些最有才能的、最训练有素的、最生气勃勃的公民赶出了英国,而使美国和别的国家大受其益,它们使这些人有更好的机会为自己的利益发挥才能。最后,谁能怀疑平等运动对工作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就是英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经济增长方面大大地落后于它的欧洲邻国、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美国在促进结果均等方面没有英国走得那么远。然而,许多同样的后果已经显露出来了:例如,促进平等的措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财富以决非平等的方式进行再分配,犯罪率上升,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下降。
资本主义和平等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存在着收入和财富的严重的不平等。这使我们大多数人感到愤慨。看到一些人在奢侈挥霍,另一些人则饱尝贫困的煎熬,谁都会感慨万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流传着一种神话,说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即我们所说的机会均等,加深了这种不平等,在这种制度下是富人剥削穷人。
没有比这更荒谬的说法了。凡是容许自由市场起作用的地方,凡是存在着机会均等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都能达到过去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水平。相反,正是在那些不允许自由市场发挥作用的社会里,贫与富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宽,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种情况发生在社会地位可以世袭的封建社会,如中世纪的欧洲、独立前的印度以及现代南美洲的许多国家。也发生在社会地位取决于能否进入政府部门的实行中央计划的社会,如俄国、中国和独立后的印度。甚至发生在象这三个国家那样以促进平等的名义引入中央计划的社会。
俄国是一个由两部分人组成的国家:一边是官僚、共产党官员、技术人员组成的一小撮上层特权阶级,另一边是今天的生活比他们的祖先好不到哪儿去的广大群众。上层阶级可以进入特殊商店和学校,可以得到各式各样的奢侈品;而广大群众却注定只能享受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我记得有一次在莫斯科看到一辆大型轿车,就向向导打听它的价钱,向导说:“噢,那不出售,是专供政治局委员用的。”最近由美国记者写的几本书,极为详细地记录了俄国上层阶级的特权生活同广大群众贫困生活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下层,俄国工厂里的一个工头与一个普通工人在平均收入上的差距,也比在美国工厂大。无疑,苏联工头的收入应该更高些,因为美国工头担心的毕竟只是被解雇,而苏联工头还要担心被枪毙。
另外,中国也是一个在有政治权势的人与其他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里一些工人与其他工人之间收入悬殊的国家。一位敏锐的中国问题学者曾经写道:“ 1957 年在中国的富庶地区与贫穷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可能比世界上除巴西外的任何较大国家都大。”他援引另一位学者的话说:“这些例子说明,中国工业部门的工资结构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工资结构平等多少。”他在总结他对中国的平等的考察时说:“中国今天的收入是怎样平均分配的呢?肯定不如台湾或南朝鲜来得平均。……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收入分配又显然要比巴西和南美洲平均……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远非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事实上,中国在收入上的差别可能要比一些公认为是‘法西斯’分子当权而广大群众遭受剥削的国家大得多。”
【按: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于西元 1956 年。】
工业的进步、机器的改进、所有新时代的伟大奇迹,对于有钱人来说,关系较少。古代希腊的富翁,从现代的供水管道得不到什么好处:有跑步的仆人提水代替自来水。电视机和收音机也不足道,罗马的贵族们能够在家里享受到最好的乐师和演员的表演,能够把最出色的艺术家留在家里。现成的服装、超级市场和其他许多现代文明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不了什么色彩。他们也许欢迎运输和医疗上的改进,而其他一切西方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主要是增长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这些成就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方便和乐趣,而在过去,这些只是富人和权势者专有的特权。
1848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道:“迄今为止,所有机器发明是否减轻了人们日常的艰苦劳动,是很值得怀疑的。机器发明使更多的人过单调乏味的生活,也使更多的制造商发财致富,同时增加了中产阶级的舒适。按其性质来说,机器发明必将使人类命运发生重大变化,但目前还没有带来重大变化。”
【按:穆勒这厮思想确实很成问题。詹姆斯·斯蒂芬批评得很恰当!】
今天谁也不能再说这种话了。只要从工业世界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就会发现,目前仍然从事极艰苦劳动的,几乎只有那些开展体育活动的人。要找到日常的艰苦劳动没有被机器发明所减轻的人,那你只有到非资本主义世界去找:俄国、中国、印度、孟加拉国以及南斯拉夫的一些地区;或者到较为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去找:非洲、中东、南美洲,以及前不久的西班牙或意大利。
结论
一个社会把平等——即所谓结果均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使用强力来达到平等将毁掉自由,而这种本来用于良好目的的强力,最终将落到那些用它来增进自身利益的人们的手中。
另一方面,一个把自由放在首位的国家,最终作为可喜的副产品,将得到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尽管更大的平等是副产品,但它并不是偶然得到的。一个自由的社会将促使人们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精力和才能,以追求自己的目标。它阻止某些人专横地压制他人。它不阻止某些人取得特权地位,但只要有自由,就能阻止特权地位制度化,使之处于其他有才能、有野心的人的不断攻击之下。自由意味着多样化,也意味着流动性。它为今日的落伍者保留明日变成特权者的机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使从上到下的几乎每个人都享有更为圆满和富裕的生活。
本节内容概述
结果均等:每个人应享有同等水平的生活或收入,而且应该结束竞争。结果均等显然是与自由相抵触的。努力推进这种均等,是造成政府越来越大并使我们的自由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
同人身平等一样,机会平等也不能完全按字面来理解。它的真正含义的最好的表达也许是法国大革命时的一句话:前程为人才开放。任何专制障碍都无法阻止人们达到与其才能相称的、而且其品质引导他们去谋求的地位。出身、民族、肤色、信仰、性别或任何其他无关的特性都不决定对一个人开放的机会,只有他的才能决定他所得到的机会。
成败的关键是个人的才能,而不是出身、信仰或民族。
生活就是不公平的。相信政府可以纠正自然产生的东西是诱人的。但是,认识到我们正是从我们所哀叹的不公平中得到了多少好处,也同样是重要的。
一个社会把平等——即所谓结果均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使用强力来达到平等将毁掉自由,而这种本来用于良好目的的强力,最终将落到那些用它来增进自身利益的人们的手中。
另一方面,一个把自由放在首位的国家,最终作为可喜的副产品,将得到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尽管更大的平等是副产品,但它并不是偶然得到的。一个自由的社会将促使人们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精力和才能,以追求自己的目标。它阻止某些人专横地压制他人。它不阻止某些人取得特权地位,但只要有自由,就能阻止特权地位制度化,使之处于其他有才能、有野心的人的不断攻击之下。自由意味着多样化,也意味着流动性。它为今日的落伍者保留明日变成特权者的机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使从上到下的几乎每个人都享有更为圆满和富裕的生活。
第6章 我们的学校出了什么问题?
教育一直是美国梦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教徒的新英格兰,学校很快建立了起来。起初作为教会的附庸,而后为世俗的官方所接管。伊利运河通航之后,农民们离开了新英格兰的山区,来到富饶的中西部平原。他们在所到之处,建立起一所所学校。不仅建立了中、小学,还建立了大学和神学院。许多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从大西洋彼岸来的移民,都渴望接受教育。大多数人在他们定居的主要都市和大城市内,都不轻易放过任何受教育的机会。
最初的学校是私立的,上学全凭自愿。渐渐地,政府开始发挥较大的作用。先是在财政上给予资助,继而是建立和管理官办学校。1852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第一个强迫入学的法令,而所有的州都实行强迫入学制则是在1918年。一直到二十世纪,政府对教育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地方当局来实施的,盛行的是地区学校,由当地的学校管理委员会控制。接着,开始了所谓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主要是由于大城市内不同教学区之间的种族成分和社会成分差异太大而引起的。另外,这场运动也受到职业教育家希望发挥更大作用的影响。随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政府的扩大和权力的集中,这场运动也不断发展。
为所有人提供的、广泛的普及教育,以及为同化我们社会的新成员的公立教育,在防止分裂活动和使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能够和睦相处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对此,我们一直,而且确有理由引为自豪。
遗憾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的教育越来越走下坡路。家长们抱怨子女们所受教育的质量下降了。很多人对孩子们的身体健康越发感到担忧。老师们抱怨说,他们所处的教学环境,往往不利于孩子们学习。越来越多的老师在教课时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纳税人抱怨费用上涨。几乎没有人认为我们的学校是在向孩子们传授他们所需要的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与促进同化及创造和睦气氛的愿望相反,学校越来越成为我们从前极力避免的分裂的源泉。
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在靠近主要城市的一些富人居住的郊区,学校办得很好,许多小城镇和乡村办的学校也很出色或令人比较满意,但一些大城市内的学校则糟得令人难以置信。
“在公立教育事业中,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黑人儿童的教育,无疑是成绩最糟糕、失败最惨重的领域。与其说是使黑人儿童受教育,还不如说是使他们失掉受教育的机会。但按照政府的一贯说法,公立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却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由此看来,公立教育的确是一个双重悲剧。”
据我们看,公立教育所患的病与我们在前面和后面章节中所谈到的许多福利计划患的病是相同的。四十多年前,沃尔特·李普曼把它确诊为“社会集权过度症”,其病因在于“信念的改变,以前人们认为,由那些思想狭隘的和自以为是的人自由行使权力会很快带来专制、反动和腐朽”,……要取得进步就必须限制统治者的作用和权力,而现在人们则认为,“统治者的能力是无限的,因此,不应对政府的权力施加任何限制。”
在培养孩子方面,这种病症的表现是:作父母的无法干预孩子受什么样的教育,他们既不能直接出学费为孩子挑选学校,也不能间接地通过开展地方政治活动来改变教育制度。学校的控制权已经落到了职业教育家手中。尤其在大城市里,学校权力的日益集中和官僚主义的增加,更加重了这种病症。
在高等教育方面,私人市场的作用要比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大一些。但在那里也摆脱不了过分集权的社会的弊病的影响。1928年,在高等教育中,上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比上私立学校的学生少。1978年,上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了三倍。由于学生自己交付学费,政府在直接筹资方面的作用落后于政府在管理方面的作用。然而,尽管如此,1978年政府的直接拨款已经超过了由公立和私立学校组成的高等教育的总经费的一半。
同对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影响一样,政府作用的增加对高等教育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它所创造的环境使尽职的老师和用功的学生都难以安心学习。
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问题所在
甚至在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年代里,就已经不仅是城市有学校,而且几乎每一个小镇、村庄和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有学校。在许多州或地方都有法律明文规定要建立一所“公立免费学校”。但是,大多数学校是靠学费和私人资助来办的。市、县或州政府一般只提供一些补充资金,补足那些父母无力交纳学费或所交学费不足的孩子们的上学费用。尽管当时受教育既不是强迫性的也不是自由的,但实际上是普及的(当然,奴隶们除外)。纽约州公立学校的校长在1836年的一份报告中说:“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有理由认为,在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和专科学校受教育的孩子的人数,与五岁至十六岁孩子的总人数相等。”当然,州与州之间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总的来讲,白人家庭的孩子,不论其家庭经济条件如何,都受到了教育。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人们发动了一场运动,要用所谓免费学校来代替形形色色的私立学校。也就是家长和其他人不直接交学费,而是用纳税的方式间接向学校交学费。E.G.韦斯特广泛研究过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作用的发展情况,他认为,这场运动并不是由对教育现状感到不满的家长们发起的,而“主要是由教员和政府雇员们”发起的。免费学校运动最著名的参加者是霍勒斯·曼,在《大英百科全书》中,他被称为“美国公共教育之父”。霍勒斯·曼曾任1837年设立的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的第一任秘书长。在这以后的十二年中,他领导了一场气势磅礴的运动,争取建立一种由政府出资、由职业教育家管理的中小学教育制度。他的主要论点是,教育非常重要,因此政府有责任向每个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学校应办成非宗教性质的,应接纳所有来自不同信仰、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种族的家庭的孩子。这种普及的免费教育可以使孩子们克服由于父母贫穷造成的不利条件。“在向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霍勒斯·曼反复强调……教育是一种最好的、一本万利的公共投资。”尽管这些论点都是在增进公众利益的名义下提出的,但教育和行政管理人员对公立学校运动的支持,大部分出于自私自利的狭隘动机。他们期望,由于是由政府而不是由学生的家长直接交学费,他们将得到更牢靠的职业、更有保障的薪金收入以及对教育更大的控制权。
“尽管困难巨大,障碍重重,……但霍勒斯·曼所提倡的这种教育制度的主要轮廓在十九世纪中叶却被勾画了出来。”
从那时起,大多数孩子都上了公立学校。只有少数学生继续在所谓私立学校念书,私立学校大都是由罗马公教会或其他教会开办的。
学校体制发生了变化:以前是私立学校占多数,现在是公立学校占多数,但这一变化并不仅仅发生在美国。正如一位权威人士所说,“人们逐渐接受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教育应当是国家的职责”。他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十九世纪意义最为重大的趋势。它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仍然影响到所有西方国家的教育事业。”十分有趣的是,这一趋势最初在1808年兴起于普鲁士,并几乎同时出现于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而英国是在美国之后才出现这一趋势的。“在自由放任主义的影响下,英国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允许国家干预教育事业。”最终建立起公立学校制是在1870年,一直到1880年才实行强迫性的初等教育,直到1891年才基本上废除学费。英国同美国一样,几乎在政府接管之前,教育就已经普及。韦斯特教授颇有根据地认为,在英国由政府接管教育正如在美国的情形一样,它并不是由于家长的压力所造成,而是由于教师、行政人员和好心的知识分子的压力所造成。他的结论是,政府的接管降低了教育质量,减少了教育的多样性。
教育同社会保险一样,也是证明极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有相似之处的一个例子。贵族专权的普鲁土和法兰西帝国都是国家管理教育的先驱。美国、英国和稍后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们,则是国家控制教育的主要支持者。
在美国,公立学校体制就如同被自由市场的汪洋大海包围的一个社会主义孤岛,它的建立只是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早期对自由市场和自愿交换的不信任。它最多不过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机会均等的理想的重视。霍勒斯·曼和他的助手们巧妙地利用这种强烈的情绪,在改革运动中获得了成功。
不用说,公立学校制度并不能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而只能看作是“美国式的”。决定该制度运行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非中央极权的政治结构:美国宪法严格地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使它无法发挥重大的作用。各州把控制学校的权力大部分都留给了地方团体、小市镇、小城市和大城市内的各个区。家长密切监视管理学校的政治机构,部分地代替了竞争,同时也确保了家长们的普遍要求得以实现。
在大萧条之前,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学校区得到巩固,教育区得到扩大,职业教育者的权力越来越大。大萧条过后,公众加入到知识分子的行列,开始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能力无限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单间教室的学校和地方学校委员会的衰败就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控制学校的权力,也就很快从较小的地方机构转给了较大的地方机构,如县、市、州一级的机构,最近则转给了联邦政府。
1920年,地方拨款占公立学校收入总额的83%,联邦拨款还不到1%。1940年,地方拨款下降到68%,而目前还不足一半。剩下的经费由州政府提供:1920年州政府拨款占公立学校收入总额的16%,1940年占30%,现在占40%以上。联邦政府拨款所占百分比虽然很小,然而增长迅速,目前已经从1940年的不到2%上升到8%左右。
由于职业教育者接管了教育的权力,家长的控制权被削弱了。另外,赋予学校的职责也改变了。人们仍然希望学校教会孩子们读、写、算,并向他们传授基本的价值概念。但是,现在学校还被认为是促进社会流动性、加强种族结合的手段,而且认为可以用它来达到其他一些与学校的基本任务关系甚少的目标。
在第四章,我们谈到过马克斯·甘蒙博士的“官僚替代论”,这是他考察完英国的全国卫生局后提出来的。用他的话来讲,在“官僚体制内……费用的增加将与生产的下降并驾齐驱。……这样的体制就象是经济宇宙中的‘黑洞’,它在吸收资源的同时,‘释放’的生产却在收缩。”
甘蒙的理论,完全适用于美国公立学校体制官僚主义的不断增长和权力的日益集中所产生的结果。自1971-1972学年至1976-1977学年的五年中,美国公立学校教职员工的总额增加了8%,以美元计算,每个学生的费用增加了 58%(扣除通货膨胀率后为 11%)。输入明显上升了。
学校学生人数下降 4%,同时,学校数目也减少了4%。我们相信,几乎没有读者会反对教育质量比数量下降得更厉害的说法。这是通过正式考试记录的成绩下降情况所说明的事实。输出明显下降了。
每单位输入量的输出减少,是不是由官僚主义的增长和权力的日益集中引起的呢?让我们来看下面的证据,学校区数目从1970-1971至1977-1978学年的七年中减少了17%,这可以说是权力日益集中的长期趋势的发展。至于官僚主义,我们来看稍早一些时候即1968-1969至1973-1974学年的情况,因为我们目前只能得到这段时期的资料。在这五年中,学生人数增加1%,专业人员总数增加15%,教师增加14%,而学监增加44%。
学校教育的问题并不仅仅同规模的大小有关,也就是说。学校区的扩大或每个学校学生人数的增加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因为事实证明,在工业中,规模庞大往往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改进质量。可以说,美国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大规模生产和经济学家的所谓“经济效果按规模递增”的原理。那么,为什么规模的大小对教育的影响不同呢?
其实并不是影响不同。问题并不出在教育同其他活动的区别,而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安排:是让消费者自由选择,还是让生产者说了算,而消费者没有发言权。如果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企业要想扩大,就得生产出消费者所喜爱的质高价廉的产品。企业单单靠规模庞大是不能把消费者不喜欢的产品推销出去的。通用汽车公司的庞大规模并不妨碍它继续发展。而格兰特公司的庞大规模也不能使它免于倒闭。在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只有当庞大规模产生效率时,它才能存在下去。
但一般来说,在各种政治安排中,规模的大小确实会影响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单个公民会感觉到,自己在较小的地区内比在较大的地区内对政治当局的所作所为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他可能不具有买东西时的那种选择自由,然而,他至少具有相当可观的机会去左右周围发生的事情。另外,假如有很多小地区的话,个人就可以选择在哪里生活。当然,这是牵涉到很多因素的复杂选择。尽管如此,它意味着地方政府必须向它的公民提供与他们所纳税款的价值相符的服务。否则,它就会被取代,或者失掉一些纳税人。
但是,当权力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时,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单个公民感到,自己对于高高在上的、缺乏人情味的政治当局没有,或很少有任何发言权。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的可能性虽然还存在,但已经是极为有限的了。
【按:这从侧面反映出要建设大同社会必须要重视地方自治。】
在学校教育中,家长和儿童是消费者,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是生产者。学校教育的集中化意味着教育单位的规模越来越大,消费者的选择能力越来越小,生产者的权力增加。教师、管理人员和联邦政府官员们同别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可能也是家长,衷心地希望有一个好的教育体制。然而,作为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联邦政府官员,他们的利益与他们作为家长的利益和他们所教的孩子的家长的利益是不同的。他们的利益是靠更大的集权化和官僚化来增进的。尽管这与家长的利益并不一致,然而,他们的利益确实是通过削弱家长的权力来增进的。
每当政府官僚们不顾牺牲消费者的选择来接管某件事时,就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情况在邮政方面、垃圾收集方面或其他章节所列举的许多例子中,比比皆是。
在学校教育中,我们中间那些高薪阶层的人们仍然享有选择自由。他们可以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他们实际上为孩子交两次学费。一次是为资助公立学校体制纳税,另一次是为自己孩子上学交学费。另外,他们也可以根据公立学校的质量,选择居住地点。好的公立学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比较富裕的郊区。在那里,家长对学校仍有控制权。
情况最糟的是大城市的城区,如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和波士顿等市的城区。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只有付出极大的努力,才交得起双重学费,因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只能让孩子上教会学校。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他们把家搬到有好学校的地方。他们的唯一办法是力图影响主管公立学校的政治当局。然而,这样做通常是徒劳的,或者是困难很大的,而且他们根本无力做这种事。市内居民在孩子的上学教育方面恐怕要比所有其他方面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唯一的例外也许是防止犯罪,这是政府提供的另一项“服务”。
具有讽刺意味而且十分悲惨的是,一个致力于使所有孩子掌握共同语言,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的制度,实际上却在加深社会的分化,而且造成了极不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市内每个学生的教育费往往与富裕郊区的一样高,但质量却差得很远。在郊区,几乎所有钱都用在教学上,而在市内的学校,经费大部分都花在维持纪律,防止破坏,或补偿破坏所造成的损失上。一些市内学校的环境象是监狱,而不是个学习的地方。就为使子女受教育而纳税而言,住在郊区的家长比住在市内的家长划得来。
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凭单计划
即便是在市内,学校并不一定非得是现在这种样子。过去,在家长有较大的控制权时,情况不是这样。今天,在那些家长仍能控制学校的地方,情况也不是这样。
美国人我行我素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提供了许多很好的例子,说明家长能有更多的选择时会出现什么情况。现举我们参观过的一个教会小学为例,该学校名叫圣约翰·克里索斯姆小学,位于纽约市布朗克斯区最贫穷的一个街道内。它的经费一部分来自一个叫做“纽约市奖学金基金会”的慈善机构,一部分来自罗马公教会,其余来自学生所交纳的学费。孩子们上这个学校,是家长的选择。这些孩子几乎都来自穷苦家庭。然而,他们的父母至少都要交纳一定数量的学费。这些孩子品行端正,求知欲强。教师专心任教。校园里非常宁静,没有噪杂的吵闹声。
甚至把那些身为修女的教师们所提供的无偿服务的费用计算在内,每个学生的花费也比公立学校的学生少得多。然而,这些孩子的平均分数却比公立学校的同年级学生高出两个等级。这是由于教师和家长可以自由选择如何教育孩子的方法。私人资金代替了税款,官僚手中的控制权被夺走,归还给了应该掌握控制权的人。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中等教育方面的例子。本世纪六十年代,哈莱姆区暴力活动猖撅。很多孩子离开了学校,一些为此而担忧的家长和教师决定设法改变这种情况。他们用私人资金买下了几家空店铺,办起了所谓沿街学校。其中最出色和最成功的一所,名叫哈莱姆预备学校,专门吸收不能用传统方法进行教育的年轻人。
哈莱姆预备学校缺乏足够的物质条件。很多教师不具有教公立学校所要求的文凭。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把事情办好。尽管许多学生过去功课很差,曾经中途退学,但是,在哈莱姆预备学校,他们找到了所期望的教育。
这所学校办得非常成功。许多学生考上了大学,而且有些考上了第一流大学。遗憾的是,它并没善始善终。在经历了最初阶段的经济危机的打击后,学校又面临着缺少现金的困难。教育委员会提出给予卡彭特(该校校长和创办人之一)一笔款子,条件是他今后按照该委员会的规章制度办事。在为保持独立性作了长期斗争后,卡彭特让步了。学校被官僚接管。“我觉得”,卡彭特先生评议道,“在教育委员会的僵化的官僚主义统治下,象哈莱姆预备学校这样的教育机构一定会夭折,不会发达兴旺的。……对于将要发生的一切,我们只能等着瞧。我不相信事情会有任何转机。我是正确的,自从我们隶属于教育委员会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不都好,也不都坏,但毕竟是弊多利少。”
这类私人冒险是有价值的。但它们最多只是触及了那些所要做的事情的皮毛而已。
一种能够取得较大进展的、把知识带回课堂的办法是,给予所有家长以较大的控制孩子教育的权力,就象我们中间那些高薪阶层的人们现在实际上具有的那样。这样做,对于那些目前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的父母,尤其重要。比起别人来,父母总是更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也更清楚自己子女的能力和需要。社会改革主义者,特别是教育改革主义者,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父母,特别是那些贫穷的、受过很少教育的父母,不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而且不具有为自己的子女选择教育的能力。这纯粹是无稽之谈。这样的父母确实很少有为子女选择的机会。但是,美国历史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一旦有机会的话,他们为了子女的幸福,总是愿意作出很大的牺牲,而且会作出很明智的选择。
无庸置疑,一些父母不太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缺乏明智地进行选择的能力和愿望。然而,他们是极少数。遗憾的是,我们的现行制度在帮助他们的子女方面所做的事,无论怎样说都是太少了。
一种既能保证父母享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又能保持现有的财政来源的简单、可行的方法是实行凭单计划。假设你的孩子正在上一所公立小学或中学。就全国范围来讲,1978年纳税人(你和我)平均要为每个入学儿童付大约两千美元。如果你让孩子从公立学校退学,转入私立学校,那你每年就为纳税人节省大约两千美元。但是,你得不到一点儿节省下来的钱,除非把这笔钱退给所有的纳税人,即使如此,你最多也只能少交几分钱税款。除去纳税外,你还得付私人学费,这就是促使你让孩子上公立学校的强大动力。
但是,假定政府对你说:“如果你不要我们为你的孩子出教育费,那你将会得到一张凭单,用这凭单你可以为孩子在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上学交纳一定金额的学费。”凭单上的金额可能是两千美元,或者,为了使你和其他纳税人都能分得节省下来的钱,也可能是一千五百或一千美元。但不论是二千美元还是少于这个数字,它至少可以解除一部分目前限制着家长选择自由的资金困难。
凭单计划所体现的原则正好同退伍军人领取教育津贴的原则一样。退伍军人可以得到一张只能用于教育的凭单。他可以拿这份钱随便挑选学校,只要这所学校符合政府所规定的某些标准。
家长也应被允许在任何一个愿意接受他的子女的学校使用凭单,不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也不论是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城市或州,还是在其他地区、城市或州。这样,不仅将给每位家长较多的选择机会,同时也迫使公立学校通过收学费而自筹资金(如果凭单金额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完全自筹资金;如果不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部分地自筹资金)。这样,不仅公立学校之间要展开竞争,而且还要同私立学校竞争。
这个计划并不减少任何人为教育纳税的负担。它只是在社会有责任向孩子们提供教育的前提下,给予家长较为广泛的选择余地,让他们自己决定孩子应受什么样的教育。这个计划也不会影响目前为私立学校规定的标准,这些标准是为实施强迫入学法而制定的。
我们认为,凭单计划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因为它既不影响教育经费,也不影响强迫入学法。我们主张走得更远一些。一般说来,社会越富裕,分配越平均,政府资助教育的理由就越少。无论如何,家长们担负了大部分教育费,而且毫无疑问,就获得相同的教育质量所花的费用来说,家长直接交学费要比通过纳税而间接承担教育费用来得便宜——除非教育活动同其他政府活动极不相同。然而,实际上,随着美国平均收入的提高和收入分配更加均等,政府资金在整个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重却越来越大。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是政府对学校的管理。父母的收入增加时,自然就想为孩子的教育多花些钱,但由于学校归政府管理,所以实现他们这种愿望的最简便方法就是增加公立学校的开支。凭单计划的一个优点在于它将鼓励更多的家长直接交纳学费。如果父母想在教育上多花些钱,那他们可以补足凭单金额,直接交纳学费。为救济困难学生的公共助学金仍会保留下来,但是,这同90%的孩子上学要靠政府的补助比较起来,情况是大为改观了,因为需要救济的困难学生只占5%或10%。
强迫入学法是政府掌握私立学校标准的根据。但我们弄不清,实行该法律本身有什么根据。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当我们最初泛泛谈到这个问题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实行这种法律,其理由是:“如果大多数公民不具备最低限度的文化和知识水平,一个稳定和民主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现在仍然相信这一理由。但是二十五年来关于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教育情况的研究报告表明,为获得最低程度的文化知识,大可不必采用强迫入学法。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类报告表明,在入学法实行之前,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几乎已经普及。在英国,实行强迫入学法和政府资助教育之前,中小学教育也已经几乎普及。强迫入学法同大多数法令一样,有利也有弊。我们不再相信利多于弊了。
我们意识到,这些关于政府资助教育和强迫入学法的观点对大部分读者来说也许是过于偏激了。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只是提出这种观点,而不要求读者给予全面支持的原因。我们主张实行凭单计划,这是摆脱目前做法的最稳妥的方法。
当前,唯一最有可能代替地方公立学校的是教会学校。因为只有教会能够大规模地资助学校教育,而只有得到资助的学校教育才能与“免费”学校教育相竞争。(试图出售别人丢掉的产品!)凭单计划将提供各种各样的替代物,如果它们不被政府“批准”所要求的极其死板僵硬的标准扼杀掉的话。人们在公立学校之间的选择机会将会大大增加。公立学校的规模将由它吸引的顾客的数目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当局划定的地理界限或分配学生数额来决定。凡建立非赢利性学校的家长(目前已有少数家长这样做了),政府都将确保他们得到教育经费。民间组织(从素食主义者团体到童子军以及基督教青年会)都可以建立学校并吸引顾客。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新型的私立学校将会崛起,开发广阔的新市场。
现在让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凭单计划可能带来的问题,以及人们已经对它提出的一些异议。
(1)宗教和政府问题。如果父母可以用凭单支付教会学校的学费,这是否违背了第一号修正案呢?不论这是否违背第一号修正案,重要的问题是:在中小学教育中采取一项加强宗教作用的政策是否合适呢?
最高法院对于各州资助家长送孩子上教会学校的法令一般都予以否决,尽管它还从来没有机会裁决一个既包括公立学校,又包括私立学校的成熟的凭单计划。但是,它今后很可能对这样一个计划作出裁决。很显然,最高法院采纳的计划将把与教会有关的学校排除在外,而适用于所有私立和公立学校。这样一种有限制的计划将远远胜过现行的制度,而且也不逊于一个毫无限制的计划。目前与教会有关系的学校可以通过把自己划分成两部分来达到政府所要求的条件:一部分与宗教无关,是独立的学校,可以接受凭单;另一部分带有宗教性质,主要组织课外活动和星期日活动,由家长或教会直接提供资金。
这种牵涉到宪法的问题只能由法院来解决。但是,要强调的是,领取凭单的是家长,而不是学校。根据美国军人法案,退伍军人可以自由选择罗马公教会学校或其他学校。而且据我们所知,迄今为止并没有人对此提出过第一号修正案的问题。社会保险金和福利津贴领取者可以随意在教会商店里购货,甚至可以把政府救济金捐献给教会,对此,也没有人提出过第一号修正案的问题。
无论律师和法官如何花言巧语地狡辩,我们确实认为,目前惩罚不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的家长的做法,违背了第一号修正案的精神。公立学校也在传授宗教,只不过不是信奉哪一个神的正式宗教,而是一整套价值观念和信仰,但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宗教。目前的做法剥夺了一些家长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们不相信公立学校传授的那种宗教,但却不得不为自己的子女接受这种宗教教育交纳学费,而要让孩子逃避这种宗教教育则必须花更多的钱。
(2)财政耗费。对凭单计划的第二条反对意见是,由于要为大约10%的目前正上教会学校或其他私立学校的孩子们提供凭单因而会增加纳税人为整个中小学教育所付的钱。其实,这只对那些忽视把孩子送到非公立学校的家长所受的歧视的人才成为“问题”。凭单计划的普遍实行将结束那种用税金来教育一部分儿童,而不管其他儿童的不平等现象。
不论怎么说,我们可以采用以下一种十分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使凭单金额大大低于每个公立学校学生的费用,以保持公共费用总额不变。在竞争性的私立学校上花少量的钱,很可能带来比现在在公立学校上花大量的钱更好的教学质量。这可以由教会学校每个学生的费用之低来说明。(名牌贵族学校收费高昂也不值得奇怪,正象1979年“二十一家俱乐部”对它的第二十一只汉堡包收费超过十二点二五美元一样,这并不意味着麦克唐纳饭店不能以四十五美分的高价出售汉堡包,或以一点零五美元的高价出售“大麦克”。)
(3)欺骗的可能性。谁能确保凭单用来给孩子交学费,而没有用来给爸爸买啤酒或给妈妈买衣服呢?我们的回答是应该把凭单的使用范围限制在已经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只允许在这类学校中将它兑换成现金。这不能防止所有欺骗行为(因为政府官员可能把它作为“酬金”送给家长),但是,它将把欺骗行为控制在一个可以容忍的范围内。
(4)种族问题。有一段时期,南方一些州为防止白人和黑人享有同等待遇而实施了凭单计划。这样做被判为非法的。防止公立学校在实行凭单计划时采取歧视做法也是非常容易的:政府将只兑换那些没有歧视行为的学校的凭单。研究凭单计划的学者遇到的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由于持有凭单的人可以自由选择学校,这就有可能增加校园内的种族隔离和阶级隔离,从而加剧种族冲突,而形成一个日益分裂和等级更加分明的社会。
我们认为,凭单计划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它会缓和种族冲突,促成一个黑人和白人为共同的目标而合作的社会,同时,又将互相尊重各自的权利和利益。许多人之所以反对强迫的种族合并,并不是出于种族主义情绪,而是因为他们多少有些担心孩子的人身安全和教学质量受到影响,这种担心也是很有理由的。如果种族合并不是靠强制,而是靠自由选择产生的话,那才是最成功的。非公立学校、教会学校和其他类型的学校,常常站在消灭种族隔离的前列。
一些公立学校发生暴力行动,仅仅是由于政府强迫人们上指定的学校造成的。只要给予学生足够的选择自由,无论是黑人学生还是白人学生,无论是穷人家出身的学生还是富人家出身的学生,无论是北方学生还是南方学生,都会离开那些不能维持纪律的学校。那些培养无线电和电视技术人员、打字员和秘书或无数其他专业人材的私立学校,很少发生纪律问题。
让其他学校象私立学校那样专业化,共同的利益就将战胜肤色的偏见,实现比目前更为广泛的种族平等。种族平等将成为现实,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凭单计划的实行,将废除为大多数黑人和白人共同反对的用校车接送学生的制度。也许人们还会用校车接送学生,而且接送的学生可能会更多,但这将是自觉自愿的,正象今天接送孩子上音乐课、舞蹈课那样。
黑人领袖不支持凭单计划的态度,是我们长期以来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他们的选民从凭单计划中得到最多的好处。这将给予他们控制子女上学受教育的权力,摆脱各级官僚机构的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摆脱教育机构的顽固控制。黑人领袖们通常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私立学校去读书,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帮助别人也这样做呢?我们怀疑这是因为凭单计划将使黑人摆脱其政治领袖的控制。这些领袖通常把教育的控制看作是获得政治支持和权力的来源。
【按:黑人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在《财富贫穷与政治》中也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
然而,由于向广大黑人群众的子女开放的教育机会日益减少,越来越多的黑人教育家、专栏作家和其他社会团体的领袖们已经开始支持凭单计划。争取种族平等会议已把支持凭单计划作为其主要的政策目标。
(5)经济等级问题。凭单计划将对社会和经济等级结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也许是研究该计划的人们分歧最大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公立学校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象是一个熔炉,使富人和穷人,本国人和外国人,黑人和白人能够融洽地生活在一起。这种情形在小社区内,过去和现在都是真的,但在大城市里,却几乎全然不是这样。在那里,由于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和收取的学费同所在地区关系很大,因而造成了居民的分化。所以毫不奇怪,国内大多数名牌公立学校都设在高收入居民区之中。
在凭单计划下,大多数儿童很可能仍将上附近的小学,而且就近入学的人数肯定要比现在多,因为该计划实施后将不再用校车强迫接送学生。但是,由于凭单计划将使各居民区的组成更加参差不齐,因而某一地区内的学校种类可能要比现在多得多。中等学校的等级几乎肯定要比现在少。侧重某一方面的学校,如艺术学校、理科学校或外语学校,将广泛地吸引来自各个不同居民区的学生。当然,自愿选择仍将严重地影响学生的阶级组成情况,但这种影响将比今天的小得多。
对于凭单计划,人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家长是否能够并乐意“添补”凭单金额。如果凭单金额为一千五百美元,家长可能另外添上五百美元,把孩子送到学费为两千美元的学校。但有人担心,由于广大中等和高等收入的家长愿意添补不足的学费,而收入低的家长拿不出钱,结果,凭单计划可能在提供教育机会上造成比现行制度更大的不平等。
这种担心致使一些支持凭单计划的人提议禁止“添补”。
孔斯和修格曼写道:
私人添补学费的自由,使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不能接受弗里德曼的计划。……无力添补学费的家庭将不得不去上那些凭单之外不再另收学费的学校,而比较富裕的家庭则可以自由地在学费高昂的学校中进行选择。今天全靠私人资金和个人财富进行的选择,明天将会变成一种由政府资助的、令人反感的特权。……这违背了一项基本的价值准则,即:任何提供选择自由的计划必须保证所有家庭的孩子享有同等的上某一所学校的机会。
弗里德曼的看法是:在一项允许添补学费的提供选择自由的计划下,穷困家庭的处境可能要比他们今天的处境强一些。然而,不论该计划将使这些家庭的教育得到多大改善,政府有意识地资助经济分离的做法,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弗里德曼的计划是政治上唯一可行的计划,那我们不会对它抱有多大热情。
对我们来说,这种观点似乎是前一章讨论的那种平等主义的一个例证:宁让父母把钱花在放纵的生活上,也不让他们把钱用在改善自己子女的教育上。这种观点在孔斯和修格曼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他们曾在另外的场合说过:“以牺牲个别的孩子的发展为代价的平等的许诺,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平等主义的最终腐败,不论其本质上有任何好的东西。”这是一种我们衷心赞同的情绪。但我们认为,从凭单计划中受益最大的是非常贫穷的人。一个人怎么能够避免“政府资助”所谓“经济分离”,就闭眼不看它“使穷人的教育得到了多大的改善”,而自以为是地为反对凭单计划的意见辩护呢?即使能够确实证明这种计划带来了某种程度的“经济分离”,也不能这样做,更何况这根本就不是事实呢。相反,通过大量的研究使我们相信,它将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另外,我们要指出的是:“经济分离”这个词的意思非常含糊不清,难以明白它所表达的确切含义。
平等主义对人们的影响是非常强烈的,以至赞成有限的凭单计划的人甚至不同意试一试无限制的凭单计划。但是,据我们所知,除了有人毫无事实根据地宣称无限制的凭单制度将导致“经济分离”外,再没有人提出过任何别的理由。
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是知识分子往往小看贫穷家长的又一证明。即使最穷的父母也能(而且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积蓄几个钱来改善子女的教育状况,尽管这笔钱不足以支付当前公共学校的全部学费。我们估计,穷人家庭也会象其他人家一样添补学费,尽管添补的数额可能较小。
如前面指出的,我们认为一项无限制的凭单计划将是改革现行教育制度的最有效的途径。这种教育制度非改革不可,因为正是这种制度注定了市内的许多孩子过贫穷悲惨的、行凶犯罪的生活。这项计划还将摧毁现行经济分离的大部分基础。在这里,我们无法提供这种见解的全部根据,但只要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早先的一个论断,就能显示我们的看法的合理性:在各经济集团所获得的各种商品和劳务(除防范犯罪行为的保护措施外)中,有比教育质量差别更大的东西吗?对各种不同经济集团开放的超级市场,是否象学校一样在质量上差异那么显著?凭单计划几乎丝毫不会改善为富人提供的教育的质量,却可以适当地改善为中产阶级提供的教育的质量,同时极大地改善为穷人提供的教育的质量。由此我们可以肯定,穷人得到的好处,将大于某些富人或中产阶级的家庭由于能够避免为孩子交纳双重学费而得到的好处。
(6)对新学校的怀疑。这是想入非非的计划吗?现在的私立学校几乎全是教会学校或纨袴子弟学校。凭单计划会不会是只补贴了这些学校,结果把大量的来自贫民窟的学生留在质量低劣的公立学校呢?有什么理由认为会出现新的学校呢?
理由就在于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市场。目前,市、州和联邦政府每年在中、小学上花费将近一千亿美元。这个数目比餐馆和酒吧间每年花在食品和酒上的钱多三分之一。后者为各阶层和各地区的人们开办了足够的各式各样的餐馆和酒吧间。前者或甚至它的一部分也一定能开办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学校。
凭单计划将开辟一个庞大的市场,吸引来自公立学校或其他职业的许多顾客。在同各类人谈论凭单计划时,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很多人都说,“我一直想去教书(或办一所学校),但我不能忍受教育机构的官僚主义、烦琐的办事程序和公立学校普遍的思想僵化。如果实施你的计划,我愿意试着办个学校。”
很多新学校将由非赢利组织来办,其他的则由赢利组织来办。对于未来学校工业的最终结构,现在尚无法预言。这将由竞争来决定。现在可以预言的是:只有那些能够满足顾客需要的学校才会生存下去,正如只有满足顾客需要的餐馆和酒吧间才能够生存下去一样。竞争将确保它们满足顾客的需要。
(7)对公立学校的影响。把管理学校的官僚的花言巧语同实际存在的问题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全国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联合会宣称,凭单计划将会断送公立学校体制,而按照他们的说法,公立学校体制是我国民主制度的根本和基石。但他们说这些话时,从来没有列举出事实证明:今天的公立学校体制取得了预想的结果——不管早先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这些组织的发言人也从来没有说明,为什么办得那样好的公立学校会害怕私立学校的竞争?如果公立学校办得不好,为什么要反对它“垮台”。
其实,对公立学校的威胁来自其自身的缺陷,而不是它们的成就。目前,在共同利益把人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小地方,公立学校,特别是公立小学,还是办得比较令人满意的,在这样的地方,即使是最全面的凭单计划也不会对公立学校产生多大影响。公立学校将继续保持其统治地位,或许由于潜在竞争的威胁,而使它有所改善呢。但是,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公立学校办得十分糟糕的城市贫民窟内,大多数家长无疑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私立学校去读书。
这将引起一些过渡性的困难。那些最关心子女幸福的家长很可能首先把孩子转到私立学校去。尽管他们的孩子并不比剩下的孩子更聪颖,但他们将受到更多地鼓励去念书并有着更有利的家庭支持。结果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一些公立学校只剩下一些“渣滓”,他们受到的教育从质量上来说可能比目前还要糟糕。
随着私人市场接管教育事业,整个教育质量将极其迅速地提高,以至最差的学校在绝对质量上也会有所改善,尽管相对水平还是低的。正如哈莱姆预备学校和其他类似的例子所表明的,在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情,而不是使人们互相仇视,和对一切都淡漠无情的学校,许多原来的“渣滓”学生在学校的表现都是非常好的。
正如亚当·斯密在二百年前所说的:
“讲授果真值得学生到堂倾听,无论何时举行,学生自会上堂,用不着校规强制。对于小儿……为要使他们获得这幼年时代必须取得的教育,在某种程度确有强制干涉之必要。但学生一到了十二、三岁以后,只要教师履行其职务,无论哪一部分的教育,都不必要加以强制的干涉。……
未有公立机构的那一部分教育,大抵教得最好,这是值得注意的。”
凭单计划的障碍
自从二十五年前我们首次把凭单计划作为解决公立学校制度缺陷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提出以来,支持在增加。今天,一些全国性组织也表示赞成。自1968年起,先是联邦经济机会办公室,而后是联邦教育委员会,相继鼓励和资助了对凭单计划的研究工作,并且表示愿意为这方面的试验提供资金。1978年,密执安州为通过一项有关凭单计划的修正案进行了投票。1979年,加利福尼亚州展开了一场运动,要求在1980年对凭单计划进行投票表决。最近,又成立了一个非赢利性的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凭单计划。在联邦一级,有人提出法案,打算对交付给私立学校的学费实行某种程度的免税,这些法案几次险些被通过。尽管它们本身并非凭单计划,但它们却是这种计划的部分翻版,这是由于免税额是有限度的,也由于这种方法很难把无力或有很少力量纳税的人都包括进去。
教育界官僚们的自私自利,表现在他们是反对在学校教育中推行市场竞争的主要障碍。正如埃德温·G.韦斯特教授所说,这个在美国和英国公共教育事业的建立中起过关键性作用的特殊利益集团,坚决反对研究、考察或试验凭单计划的所有尝试。
黑人教育家和心理学家肯尼思·B.克拉克总结了管理学校的官僚们的态度:
……看来,为提高城市公立学校工作效率的必要改革,并不会由于它应当到来而到来。……如想了解教育机构抗拒这种改革的能力,最要紧的是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公立学校制度是很少受到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竞争的,是受到保护的公有垄断集团。批评美国城市公立学校的人,甚至包括我这样严厉的批评者,几乎没有哪一个敢于对目前公立教育组织的现状提出疑问。……也不敢对选拔学监、校长和教师的标准和水平提出疑问,不敢问一问所有这一切给公立教育的目标——即培养从事民主事业的有知识和文化的,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尊严、创造性而又尊重他人的人——带来的影响。
垄断组织根本不必关心这些问题。只要各地的公立学校可以确保得到州政府的补助和联邦政府越来越多的补助,只要它们不必为激烈的竞争节省开支,指望公立学校的效率有所提高的一切想法就是痴心妄想。如果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现行的教育制度——不包括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因为它们的发展几乎已经到头了——那么,改进公立教育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
这一估计的正确性后来被教育机构对联邦政府出资进行凭单计划的试验的反应所证实。当时许多地区主动制定了颇有成功希望的计划。但只有加利福尼亚州阿卢姆罗克一个地方的计划,经过艰苦磨难,获得了成功。我们根据亲身经历了解得最清楚的例子发生在新罕布什尔州。当时该州的教育委员会主席威廉·P.比特本德进行了一项试验。条件似乎满好,联邦政府拨了款,定出了详细计划,选出了作试验的一些地区、家长和行政管理人员也达成了初步协议。正当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当地学校的学监和其他头头却劝说一个又一个地区退出了预定的试验,结果,整个探索夭折了。
阿卢姆罗克的试验是实际进行的唯一试验,但很难说它是真正的试验。试验仅仅限于几所公立学校,而且除政府拨款外不允许家长或其他人捐款。一些所谓的小型学校建了起来,它们的课程各不相同,家长可以任选一所学校让孩子在那里上三年学。
正如负责这项试验的唐·艾尔斯所说:“所发生的意义最为重大的事情是:教师第一次有了一些权力。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安排适合学生需要的课程。州和地方学校委员会对麦卡科兰学校的课程安排不予干涉。家长越来越多地参与学校的事情,更经常地参加学校的会议。另外,如果他们看中了另一所学校,他们有权让孩子转学。”
尽管这项试验的范围有限,但由于家长可以进行更多的选择,因而对教育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考试分数上看,麦卡科兰学校从所在地区的第十三名上升为第二名。
但是,现在这项试验已经成为一件过去的事了。象哈莱姆预备学校的命运一样,教育机构断送了它。
在英国也有同样的阻力。英国的一个叫做“选区教育凭单试验之友”的非常有力量的组织,在英格兰的肯特郡的一个小镇上进行了四年的努力来推行一项试验。政府当局表示赞同,然而教育机构却极力反对。
职业教育者对凭单计划的态度,可以从丹尼斯·吉所说的话中清楚地看出来。此人是肯特郡阿什福一所学校的校长兼当地教师协会秘书,他说:“我们把这项计划看成是我们与家长之间的一道障碍。他们拿着小纸片(即凭单)来找你,指使你干这干那。我们之所以要对一些事情作出判断,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样做对每个孩子最有利,而不是因为有人说:‘要是你们不干,我们就自己干。’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市场上的那种生意经。”
换句话说,吉先生反对让顾客(在这里指家长)决定自己的子女应受什么教育,而想让官僚们来决定。
吉先生说:
“我们通过管理机关向家长负责;通过检查人员向肯特郡议会负责;通过女王的检查官向国务大臣负责。这些人是能够作出正确判断的内行和专家。”
“我不能肯定家长都知道什么样的教育对他们的孩子最有利。他们知道给孩子吃什么最好,知道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对孩子最有益。但我们学的却是弄清孩子们身上存在的问题,发现他们的弱点,纠正那些需要纠正的毛病。我们希望在家长的协助下,而不是在不正当的压力下,自由地干这些事。”
不消说,至少有一部分家长是对此持不同看法的。住在肯特郡的一位电工和他的妻子为使他们的儿子上一所他们认为最适合于他的学校,竟与官僚们斗争了一年的时间。
莫里斯·沃尔顿说:
“我认为,在现行教育制度下,当家长的没有一点选择的自由。他们要由教师来告诉怎样做才最有利。他们被告知说,教师们正在从事伟大的工作,对此不要多加过问,如果实行凭单计划的话,我认为它将使教师和家长结合在一起,使他们的关系密切起来。为自己的子女感到担忧的家长,会把自己的孩子从办得不好的学校转到办得好的学校去。……如果一所学校一无是处,存在着破坏公共财产的现象,而且纪律非常松弛,学生无法念书,那它会因此而垮台,在我看来,这倒是件好事。
“眼下,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教师把它当作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但同时又用它作紧箍咒套在家长们的头上。家长找到教师说,我对你们的教学不满意。但教师会相当粗暴地回答说,你不能把孩子带走,也不能给他转学,你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走开,别来麻烦我。这可能是今天某些教师新采取的态度,而且他们确实常常这样对待家长。但是,现在(有了凭单计划以后),他们的地位颠倒过来了,只有家长们能大声大气地对教师讲话:让他们卖力气干活,让家长的钱花得上算,能够更多地参与学校事务。”
尽管教育机构坚决反对,但我们相信,凭单计划或其他类似的计划将很快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被采纳。我们对教育事业要比对福利事业更乐观,因为教育同我们许多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比起消灭救济金分配上的浪费和不公平来说,我们愿意尽更大的努力来改善孩子们的教育状况。对教育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就我们来看,目前减少这种不满情绪的唯一途径是使家长有更大的选择。这是切实可行的措施。尽管凭单计划一直受到抵制,然而,却一再被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提出来。
高等教育的症结
同初等和中等教育一样,今天存在于美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也是双重的:既有质量问题,又有平等问题。在这两个方面,由于没有强迫入学制而使问题大为改观。法律没有规定某人必须上大学,因此,对有志继续受教育的学生来说,在上哪所大学方面,他们可以进行广泛的选择。广泛的选择减轻了质量问题,但加剧了平等问题。
质量:由于没有人违背自己的意志(或其家长的意愿)上一所学院或大学,因此,任何一所大学要想办下去,就得满足学生的最低要求。
这里存在着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在收学费低的官办学校,学生是二等顾客。他们是部分靠纳税者花钱资助的慈善事业的施舍对象。这一特征影响到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
收学费低的事实意味着,市立和州立的高等学校除了吸引许多想接受教育的、用功的学生外,还吸引了许多其他男女青年,他们来这里是因为学费低,有住宿和伙食补贴,能同其他年青人在一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只不过是高中毕业但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时的一段令人愉快的歇息期。上课、考试和取得毕业分数并不是他们来上学的主要理由,而是他们为获得其他好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由此而带来的一个结果是退学率很高。例如,在国内公认的最好的州立大学之一,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中,被录取的学生中大约只有一半人完成整个大学的学业,而这在官办大学中,毕业的比率还算是高的呢。当然,有些学生退学后又转上了其他学校,但这只对退学总人数产生很小的影响。
另一结果是,课堂上的气氛往往使人感到压抑,而不能激发学习的热情。当然,各学校的情况并非千篇一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课程和教师。各个学校内用功的学生和尽职的教师总可以想办法凑到一起,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同上述情况一样,这只能对所浪费的时间和税款起很小的补偿作用。
在市立和州立大学中,不仅有勤奋的学生,而且有优秀的教师。但是,在有名望的官办学校中,对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的酬劳办法是不利于那里的教学的。教师们靠研究和出版成果来提升,管理人员靠从州立法机关那里争取到更多的拨款来擢升。结果,甚至最有名的州立大学,如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的威斯康星大学或密执安大学并不以其教学质量闻名。它们是以培养研究生的工作、科研工作和体育运动队而出名的,这才是给它们带来好处的地方。
私立大学的情况颇不相同。这些学校的学生需要付很高的学费,即使学费支付不了大部分教育费,也可以支付相当一部分教育费。所交学费来自家长、学生自己挣的钱、政府贷款以及奖学金。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学生成了一等顾客;他们为得到的教育而付钱,因而他们想要得到与他们所付的钱价值相等的教育。
学校出售教育,学生购买它。同在大多数自由市场上的情形一样,买卖双方都受到强烈刺激来为对方服务。如果某一大学不能提供学生所指望的那种教育,他们就会上别的大学。学生想得到他们所付学费的全部价值。正如一位在颇负盛名的私立大学达特默思学院上学的学生所说:“当你想到修一门课程要花三十五美元,而又考虑到用这三十五美元能干其他事情时,你肯定会专心致志地听课。”
一个结果是,上私立大学的学生完成大学学业的人数,大大多于公立大学完成大学学业的人数。达特默思学院的毕业率为95%,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毕业率仅为50%。达特默思学院的比率在私立大学中可能是较高的,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比率在官办大学中也是较高的一样。尽管如此,它们之间的差距也还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样来谈论私立院校是过于简单了。除教育外,它们还出售另外两种产品:纪念物和研究工作。个人和基金会捐赠了私立院校的大部分建筑和教学设备,资助了教授职位和奖学金。大部分研究经费来自捐赠、联邦政府的特别拨款或其他来源。捐赠者出钱,是因为他们想促进某件他们认为值得促进的事情;另外,以个人命名的建筑、教授职位、奖学金也可以纪念某位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它们称为纪念物的原因。
出售教育和出售纪念物能够结合在一起,说明自愿合作具有被人们大大低估了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通过市场的作用可以利用人们自私自利的动机来为广泛的社会目标服务。亨利·M·莱文在谈到高等教育的筹资问题时写到:“人们怀疑:这个市场是否会资助古典文学系或其他许多人文学科方面的教学计划。这方面的教学活动可以促进文化知识的发展,而人们普遍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文化知识的发展将广泛地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使这些活动维持下去的唯一途径是靠直接的社会补贴。”这里的所谓补贴指的是政府拨款。莱文先生显然是搞错了。广义上的市场,一直维持着私人机构的社会活动。正因为这些活动对整个社会有益,而不是只为捐赠人的眼前私利服务,才使得它们对捐赠人具有吸引力。假设某某太太想为其丈夫某某先生增添荣誉,那么,她或别人是否会认为只要让某一大型工业企业(这可能是这位先生的真正纪念物和对社会福利事业的真正贡献)用这位先生的名字命名一座新建的工厂就行了呢?他们显然不会这样认为。另一方面,如果这位太太出资帮助一所大学修建一座以其丈夫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或建筑物,或资助以其丈夫的名字命名的教授职位或奖学金,那就会真正被认为是对其丈夫的赞颂。它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确实提供了一项社会服务。
学生们以两种方式参加制造教学、纪念物和研究工作的合资企业。他们既是顾客,又是雇工。他们靠促进纪念物和研究成果的出售,为教学基金作出贡献,从而获得他们的一部分教育。这是说明自愿合作的途径和潜力是多么复杂而又难以捉摸的另一个例子。
许多名义上官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实是一种混合体。它们收学费,从而把教学卖给学生。它们接受盖建筑物的捐赠,从而出售纪念物。它们同政府机构或私人企业签订研究合同。很多州立大学得到大量的私人捐赠,如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密执安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这些只是其中的少数几个。我们的印象是:一般来说,市场的作用越大,学校的教学也就搞得越好。
平等。使用税款来资助高等教育的理由通常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莱文先生在上面提出来的:高等教育除了给学生本身带来好处外,还产生“社会福利”。第二个理由是说,为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需要政府的资助。
(1)社会福利。当初我们第一次论述高等教育时,我们对第一种理由是抱有极大同情的。现在则不然了。从那时到现在,我们一直力图引导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搞清楚他们所说的“社会福利”到底指的是什么。然而,得到的回答几乎总是很差劲儿的经济学概念。我们被告诉说,国家可以因为拥有更多的掌握高超技术和受过良好训练的人而得到好处;为得到这种技术水平而进行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更多的受过训练的人可以提高其他人的生产率。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但是,没有一条可以成为补贴高等教育的正当理由。这些说法也同样适用于有形资本(即机器、厂房等),但是,没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用税款来补贴通用汽车公司或通用电器公司的资本投资。如果高等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经济生产率,那么人们可以通过收入的提高获得由此而产生的好处,因而个人的私利刺激人们去接受高等教育。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无形的手会使人们的个人利益服务于社会利益。靠补贴教育来改变他们的个人利益的做法本身违背了社会利益。那些只愿意上有补助的学校的多余的学生,恰恰是那些认为得到的好处低于所付的学费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会愿意自己付学费了。
偶尔得到的回答是很好的经济学概念,但它们所依据的常常是武断的假设而不是有根有据的事实。最近的一个例子见于由卡内基基金会建立的高等教育专门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在最后的一份题为《高等教育:谁付钱?谁受益?谁应该出钱?》的报告中,该委员会对所谓的“社会福利”作了总结。该报告中包括上面一段讨论过的不恰当的经济论据——也就是说,它把受教育的人得到的自然增长的福利,当成是第三者得到的福利。但是,它也列举了一些所谓的好处。如果这些好处确实存在的话,它们将增加那些并非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福利,由此而可能证明政府补贴高等教育是有道理的。它列举的好处有:“知识的总进步……;民主社会的更大的政治效能……;由个人和集团之间更好的了解和相互谅解所取得的更大的社会效能;对文化遗产更有效的保护和发展。”
卡内基委员会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至少对可能产生的“高等教育的不良后果”在口头上谈了谈,尽管所列举的例子只是“由当前多余的博士学位(这不是社会,而是个人造成的)所引起的个人的失败情绪和在过去由于校园里爆发的混乱而引起的公众的不悦。”读者应注意,他们列举的好处和“消极后果”,经过多么仔细的选择,带有多么深的偏见。在印度那样的国家,大批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成了社会和政治极度不稳定的根源。而在美国,“公众的不悦”几乎算不上是“校园混乱”所带来的唯一的或主要的消极后果。更为重要的后果是对大学的管理、对“民主社会的政治效能”,以及对“通过……更好的了解和相互谅解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产生的有害影响,而这些都是该委员会毫无保留地列举出来的高等教育给社会带来的好处。
该报告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它认识到,“即使没有政府补贴,高等教育给社会带来的某些好处也会作为私立教育的副作用而出现。”然而,这也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尽管该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的很费钱的专门研究,但是,它并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态度去鉴别各种所谓的社会效果,没有从量的方面粗略地估计它们的重要意义,也没有粗略地估计一下。如果政府不提供补贴会产生多少社会效果。结果,它提不出任何证据,来说明总的社会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更不必说能够充分证明花在高等教育上的数十亿美元的税款是否取得了任何真正的积极效果。
该委员会满足于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没有任何精确的——甚或不精确的——方法能够估计出个人和社会从个人和政府开支中得到了多少好处。”然而,这并不妨碍它坚决地、毫不含糊地建议增加早已是非常庞大了的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补贴。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特殊要求。卡内基委员会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前校长克拉克·科尔领导。在包括科尔在内的由十八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中,有九人现在担任或曾经担任过高等学府的校长,另外五名成员任职于与高等教育机构有关的部门。剩下的四人曾在大学的董事会或评议会里干过事。当工商业者高举着自由企业的旗帜,呼吁得到关税、定额或其他方面的优惠向华盛顿进军时,学术界会很容易地看出这是一种特殊要求,从而对之加以嘲笑。如果一个钢铁工业委员会有十八名成员,其中十四名来自钢铁工业,而它建议增加政府给予钢铁工业的补贴,学术界又会说些什么呢?我们至今还未听到学术界对卡内基委员会的建议发表过任何意见。
(2)教育机会的均等。促进“教育机会均等”是通常为使用税款资助高等教育辩护的主要理由。用卡内基委员会的话来说,“为了使教育机会尽可能地均等,我们赞成让公众暂时为教育多掏一些钱。”用卡内基基金会的话来说,“高等教育是通向更广泛的机会均等的主要途径。它越来越为出身贫寒的人、妇女和少数民族所拥护。”
这一目标是可嘉的,事实的叙述也是正确的。但是,它们之间缺少一个中间环节。政府的补贴是促进了还是阻挠了目标的实现?高等教育是否由于有了政府补贴才成为“通向更广泛的机会均等的主要途径”,还是没有这种补贴也能促进机会均等呢?
卡内基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的一组简单统计数字说明了问题:1971年入私立大学的学生中,20%来自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17%来自收入在五千——一万美元之间的家庭;25%来自收入超过一万美元的家庭。换句话说,私立大学为来自家庭收入最低和最高的青年男女提供了比官办大学更多的机会。
而这仅仅是冰山之巅。来自中等和上等收入家庭的青年上学的人数为来自低收入家庭青年的二倍或三倍,而且,他们往往上收费较高、学制较长的大学(他们通常上四年制的专科或本科学校,而不上两年制的初级大学)。结果,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从政府补贴中受益最多。
【作者按:卡内基委员会:《高等教育》,第176页。书中的数字不是根据卡内基委员会制作的表格计算的,而是根据该委员会引用的资料来源:美国1971年国情普查报告P-20,第241号,第40页,表140我们在计算时发现卡内基报告中的数字有些小错误。我们给出的数字多少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与配偶住在一起的已婚学生是按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配偶的家庭的收入归类,而不是按他们父母的收入归类。如果除开已婚学生,数字会更大: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的孩子有22%上私立学校,收入在五千至一万美元之间的家庭为17%,收人高于一万美元的家庭为25%。根据美国国情普查局的数字,在1971年在校的十八至三十四岁之间的公立院校学生当中,来自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的学生不到14%,虽然在这一年龄组,22%以上的人来自这些低收入家庭。57%的公立院校学生来自收入高于一万美元。】
一些出身贫穷的青年确实从政府补贴中得到了好处。一般说来,他们是穷人中生活境况较好的人。他们具有的天赋才能和技能使他们能从高等教育中受益,这种技能甚至能使他们用不着上大学就能挣到较高的工资。不论怎样,他们注定要成为穷人中境况好的人。
这里有两份详细的研究报告,一份是关于佛罗里达州的,另一份是关干加利福尼亚州的,它们说明了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从面向低收入阶层转向高收入阶层的程度。
佛罗里达州的研究报告把四个收入阶层中的每个阶层在1967-1968年度中从政府高等教育经费中得到的全部好处与他们以纳税形式所花的钱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只有最高收入阶层得到了净收益,这个阶层得到的好处比他们付的钱多60%。最下面的两个阶层付的钱比他们得到的好处多40%;中等阶层付的钱比他们得到的好处多20%以上。
1964年关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研究报告,也得出了令人吃惊的重要结论,不过表达方式稍有不同,它所比较的是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和没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得到了相当于他们平均收入1.5-6.6%的纯收益,得好处最多的是那些有孩子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念书而且平均收入最高的家庭。没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平均收入最低,而且还要从他们的收入中拿出8.2%资助高等教育。
事实是不容置疑的。甚至卡内基委员会也承认,高等教育经费的再分配产生了违反政府意愿的结果,不过,人们必须非常仔细地阅读卡内基委员会的各份报告,才能在下面这样的话语中发现他们的这种态度:“一般说来,这一‘中等阶层’……得到的公共补贴是相当可观的。通过补贴的合理的再分配,我们可以达到更大的公平。”该委员会提出的主要对策还是老一套:进一步增加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开支。
就我们所知,似乎没有比政府资助高等教育更为不平等的政府计划了,也没有哪一项计划能更清楚地说明“董事规则”。我们这些中等收入和高等收入阶层的人们,诱骗穷人大规模地补贴我们,然而,我们不仅丝毫不感到耻辱,反而大吹大擂我们的大公无私精神。
【按:这里有个表格,对内容没有太大影响,故删去。】
高等教育:解决办法
每个男女青年,无论其父母收入、社会地位、居住地区或种族怎样不同,只要愿意现在交付学费或愿意毕业后用挣得的较高工资来补交学费,都应得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为确保所有的人都有上学的机会,有充足的理由提供足够的贷款,有充足的理由传播有关这种贷款的消息。并敦促经济情况较差的人们去利用这一机会。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让那些没有享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为享受高等教育的人掏腰包。如果是政府经管高等教育机构,它收取的学费应该相当于向学生提供的教育和其他服务的全部费用。
虽然确实应该废除纳税人为高等教育出钱的做法,但目前这在政治上似乎是办不到的。为此,我们将附带论述一项代替政府出资的、不那么激烈的改革方案——高等教育凭单计划。
代替政府出资的办法。由于大学生毕业后收入的差别很大,因此,以固定金额的贷款资助上大学的青年是有缺陷的。有些人干得很好,偿还贷款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有些人最终只能挣得有限的收入,偿还贷款对他们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在教育上花钱就是对一个有风险的企业进行投资,也可以说是对一个新建立的小企业进行投资。资助这种企业的最佳方法不是提供固定数额的贷款,而是对其股本进行投资,即“买进”某企业的股票,将来按股分红。
对于教育来说,就是“买进”某人未来的一部分收入,也就是说,如果某人同意在未来的工资中拿出一规定部分还给投资人,投资人就预付给他上学所需要的资金。采用这种方法,投资人可以从比较成功的人那里收回多于他当初投资的钱,从而补偿在那些不成功者身上投资损失的钱。按这种方式签定个人合同虽然在法律上似乎没有障碍,但这种方法并没有被人们普遍采用,我们猜测,其主要原因是这种合同的期限很长,实施起来费用高,困难多。
二十五年前(1955年),我们提出过一项计划,建议通过某一政府机构对高等教育进行所谓“资本投资式的”资助。该机构可以向任何符合最低质量标准的个人提供或帮助他们筹集上学所用的资金。它将在规定的年限内每年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条件是所提供的资金必须用于在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高等院校接受教育。反过来,个人将同意从他未来的超过一定数额的收入中,提取一定的百分比,偿还他从政府那里得到的资金。偿还给政府的钱可以很容易地与所交纳的所得税结合在一起,因而额外牵涉到的行政管理费是非常少的。偿债基额应与未受高等教育的人的平均收入相等;每年应偿还的数额要加以仔细的计算,以使整个方案能自给自足。这样,实际上使入学者负担了全部学费,投资金额就可以由个人的选择来决定了。
最近(1967年),一个专门研究小组建议实施一项与我们的计划相类似的计划,其名称很吸引人,叫做“教育机会银行”。该小组是约翰逊总统下令成立的,组长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杰罗尔德·R·扎卡赖亚斯教授。它对这项计划的可行性和为使其能够自足自助所需要的费用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该计划遭到了“州立普通大学及农业大学联合会”的猛烈攻击,想必本书读者是不会对此感到奇怪的。这正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私自利的谬说”的一个极好例证。
1970年,卡内基委员会提出了资助高等教育的十三条建议,其中第十三条提议建立一所“全国学生信贷银行”。该银行将提供长期贷款,偿还条件将部分地取决于届时的收入情况。该委员会说:“……我们认为,全国学生信贷银行不同于教育机会银行,它为学生提供补助金,而不是全部教育费用。”
最近,包括耶鲁大学在内的一些大学,研究或采纳了一些由它们自己管理的、偿还条件暂且不定的计划。由此可见,这种计划还是有活力的。
高等教育凭单计划。在用税款补贴高等教育的情况下,弊端最少的补贴方法就是前面谈到的在中小学采用的凭单计划。
让所有官办学校根据所提供的教育服务的全部费用来收学费,从而在平等的条件下与非官办学校竞争。用每年希望得到补贴的学生的人数除以每年用于高等教育的全部税款,所得的数目便是每一张凭单的金额。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选择在任何教育机构使用凭单,唯一的条件是他们所上的学校是需要补贴的学校。如果申请得到凭单的学生人数超过现有凭单的数目,就以最能为社会所接受的标准来分配凭单,如根据考试测验的成绩、体育才能、家庭收入或其他各种各样可能的标准来分配。由此可见,这种方法大致上与美国军人法向退伍军人提供教育的做法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军人法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所有退伍军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正如我们第一次提出这项计划时写道的:
采取这种方法,将更有效地促使各类学校之间开展竞争,更有效地利用它们的资源。它将消除要政府直接资助私立院校的压力。这样,一方面将使私立院校相对于州立院校获得发展,同时又使它们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和多样性。作为附带的好处,它还会起到严格控制补贴的作用。这种补贴教育机构而不是补贴人的做法,最终将导致不加区别地补贴所有大专院校的活动,而不是仅仅补贴各州认为应该补贴的活动。即使作一粗略的考察也可看出,尽管这两种活动有相互重叠的地方,但决不是一码事。
为促进公平而采用凭单计划的理由……是很明显的。……例如,俄亥俄州对本州公民说:“如果你们有小孩想上大学的话,我们将连续四年向他们主动提供丰厚的奖学金,只要他们能够满足起码的入学条件,并明智地选择上俄亥俄大学(或其他一些由本州政府资助的大学)。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想上(或你想让他们上)奥柏林学院或西部储备大学,那他一个钱也甭想得到,更不要说去上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西北大学、贝洛伊特大学或芝加哥大学了。”我们怎么能为这样一种方案辩护呢?如果把俄亥俄州打算花在高等教育上的钱花在所有高等院校的奖学金上,并要俄亥俄大学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其他院校竞争,难道不是更为公平,更能提高奖学金的水平吗?
自从我们最先提出这一建议以来,一些州相继有限度地实施了这方面的计划,颁发了可以在私立院校使用的奖学金,尽管只限于本州内的私立大学。另一方面,虽然纽约州立大学的董事会也根据同样精神制定了一项非常出色的奖学金计划,但这个计划却被该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一项宏伟计划代替了。洛克菲勒计划是要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样式办纽约州立大学。
高等教育方面的另一重要事态发展是联邦政府在资助高等教育方面的作用大大增大了,尤其是对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管理更多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干预是联邦政府活动大规模扩张的一部分。而联邦政府活动是在争取更大的民权的名义下采取的所谓“积极行动”。这种干预引起了高等院校教职员工的极大关注,他们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官员过多地干预教育。
这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遗憾的是高等教育的前途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威胁。学术界曾极力鼓吹对其他部门进行干预,只有干预到他们头上时,他们才感觉到干预带来的种种弊病:耗资巨大,学校的基本教学任务受到干扰,以及适得其反的效果等。此时,他们成了当初信仰的牺牲者,成了继续从私利出发仰给于联邦政府的牺牲者。
结论
按通常的习惯,我们把“受教育”和“上学”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但是,区别这两个词的意思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事物的本质。如果较为细心地使用这两个词的话,就会发现:“受教育”并不一定都得“上学”,“上学”也并不都“受到了教育”。许多学历很高的人并没有受到教育,而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并没有上过学。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我国的创建者当中是一位真正受过教育的、博学多才的人,然而,他只上过三、四年正规学校。这种例子举不胜举。毫无疑问,每个读者都认识一些学历很高,但他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认识一些没有上过学,但他认为很有学问的人。
我们认为,政府在资助和管理学校方面作用的不断加大,不仅导致了纳税人金钱的巨大浪费,而且导致了比自愿合作继续起较大作用所能产生的教育制度远为落后的制度。
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再没有比学校更令人不满意的机构了,几乎没有比它更能引起不满情绪,更能破坏我们的自由了。教育机构极力捍卫其现有的权力和特权。它得到了许多具有集体主义观点、热心公共事业的人们的支持。但它也受到了攻击。学生考试成绩普遍下降;城市学校中犯罪行为、暴力行动和秩序混乱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绝大多数白人和黑人起来反对用校车接送学生上学;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严密控制下,许多大专院校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感到惶惶不安,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教育事业中权力日益集中、官僚主义日益严重和社会化日益增强等趋势的严厉批判。
在这一章里,我们曾试图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采用凭单制度,该制度将给予不同收入的家长以选择子女所上学校的自由;在高等教育中采用贷款资助制度,偿还条件根据学生毕业后的收入情况来确定,该制度不仅将使教育机会均等,而且将消除目前征穷人的税来资助富人家子弟上学的不合理现象;或者,在高等教育中也采用凭单计划,该计划将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同时促使补贴高等教育的税款的分配更加公平。
【按:宋代朱子等人的教育实践及范式义庄的存在也能表明这种类型的教育制度符合儒家教育理念。】
这些计划是富有想象力的,然而,并非是行不通的。阻碍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和偏见,计划的实施和管理根本不成问题。在我国和其他国家,早已有人小规模地实施过类似的计划。公众是采取支持态度的。
这些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只要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或在目标不变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方法,我们就能够巩固我们自由的基础,并使教育机会的均等具有更为实在的意义。
本节内容概述
由于教师和家长可以自由选择如何教育孩子的方法。私人资金代替了税款,官僚手中的控制权被夺走,归还给了应该掌握控制权的人。
一种既能保证父母享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又能保持现有的财政来源的简单、可行的方法是实行及教育券计划。
教育券计划所体现的原则正好同退伍军人领取教育津贴的原则一样。退伍军人可以得到一张只能用于教育的凭单。他可以拿这份钱随便挑选学校,只要这所学校符合政府所规定的某些标准。
家长也应被允许在任何一个愿意接受他的子女的学校使用凭单,不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也不论是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城市或州,还是在其他地区、城市或州。这样,不仅将给每位家长较多的选择机会,同时也迫使公立学校通过收学费而自筹资金(如果凭单金额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完全自筹资金;如果不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部分地自筹资金)。这样,不仅公立学校之间要展开竞争,而且还要同私立学校竞争。
这个计划并不减少任何人为教育纳税的负担。它只是在社会有责任向孩子们提供教育的前提下,给予家长较为广泛的选择余地,让他们自己决定孩子应受什么样的教育。这个计划也不会影响目前为私立学校规定的标准,这些标准是为实施强迫入学法而制定的。
领取教育券的是家长,而不是学校。根据美国军人法案,退伍军人可以自由选择天主教学校或其他学校。
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采用教育券制度,该制度将给予不同收入的家长以选择子女所上学校的自由;在高等教育中采用贷款资助制度,偿还条件根据学生毕业后的收入情况来确定,该制度不仅将使教育机会均等,而且将消除目前征穷人的税来资助富人家子弟上学的不合理现象;或者,在高等教育中也采用教育券计划,该计划将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同时促使补贴高等教育的税款的分配更加公平。
下面的术可供参考:
和国内外顶级高校合作录制教学视频、实行网络教育、普及优质教育资源
国民建言形成各行业的路线图提供参考
组建巨型在线图书馆方便国民阅读
建设大型题库
官方出面购买国外大型论文库
作为教育家,柳诒徵爱才、重才,言传身教,培植弟子,“多能卓然而立”,人称“柳门成荫”。更多的人则是受到柳氏学问、道德、人格、理想的影响。在中国学术界,有说他“培养出来的文、史、地、哲各门乃至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最多”。柳氏教学之法,郑鹤声曾说,“柳先生的教学方法,以探求书本为原则。他讲中国史的时候,并不编辑课文,或某种纲要,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而指定若干惨考书籍,要我们自动地去阅读...,读了以后,要把心得记在笔记本上,由他详细批阅...他要学生平时以阅读正史(二十四史)为主,并经常从正史中出许多研究题目,要我们搜集材料,练习撰作能力,由他评定甲乙,当为作业成绩...这种治学方式,的确是很基本的,促使我们养成一种严谨笃实的学风,使我们一生受用不尽” ;张世禄回忆说他教导学生要能做“比较思考”,鼓励学生“自己找问题去钻研历史”;胡焕庸回忆他的授课“夹叙夹议,...既不是枯燥无味的考证,也没有不着边际的空谈,真可说是广征博引,有引人入胜之功”;茅以升曾说,“我从先生受业八年,感到最大获益之处,是在治学方法上从勤从严,持之以恒”。
教育思想方面,柳诒徵倡导自由教学,认为应当根本改革工厂批量生产式、机械式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以利于每一个人学生自由学习、个性发展。必修课程、标准以及教师资格可由教育部统一制定;国家组织严格的考试,各门课程及格者,授予相应文凭。学生自小学毕业后,听其自由求师。学堂停办,教师可自由授徒。同时,国家在各省市县设立公共的科学仪器馆、图书馆及各类音乐美术体育设施,适当收费或免费供学生使用。
附录《礼记·大学》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戮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附录《礼记·学记》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眾;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今之教者,呻其占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發然後禁,則捍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學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附录《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
今天所讲的问题,是怎么样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我们想研究一个什么方法,去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便不要忘却我前几次所讲的话,我们民族现在究竟是处于什么地位呢?我们民族和国家在现在世界中究竟是什么情形呢?一般很有思想的人所谓先知先觉者,以为中国现在是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但是照我前次的研究,中国现在不止是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依殖民地的情形讲,比方安南是法国的殖民地,高丽是日本的殖民地,中国既是半殖民地,和安南高丽比较起来,中国的地位似乎要高一点,因为高丽安南已经成了完全的殖民地;到底中国现在的地位,和高丽安南比较起来,究竟是怎么样呢?照我的研究,中国现在还不能够到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比较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更低一级,所以我创一个新名词,说中国是“次殖民地”,这就是中国现在的地位。这种理论,我前次已经讲得很透彻了,今天不必再讲。
至于中国古时在世界中是处于什么地位呢?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像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中的独强。我们祖宗从前已经达到了那个地位,说到现在还不如殖民地,为什么从前的地位有那么高,到了现在便一落千丈了呢?此中最大的原因,我从前已经讲过了,就是由于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国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我们想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我们知道现在是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既然知道了处于很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像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所以能知与合群,便是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大家先知道了这个方法的更要去推广,宣传到全国的四万万人,令人人都要知道;到了人人都知道了,那么我们从前失去的民族精神,便可以恢复起来。从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著觉,现在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唤醒起来,醒了之后,才可以恢复民族主义;到民族主义恢复了之后,我们便可以进一步去研究怎么样才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
中国从前能够达到很强盛的地位,不是一个原因做成的。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亚洲古时最强盛的民族,莫过于元朝的蒙古人。蒙古人在东边灭了中国,在西边又征服欧洲;中国历代最强盛的时代,国力都不能够越过里海的西岸,袛能够到里海之东,故中国最强盛的时候,国力都不能达到欧洲;元朝的时候,全欧洲几乎被蒙古人吞并,比起中国最强盛的时候,还要强盛得多。但是元朝的地位,没有维持很久;从前中国各代的国力,虽然比不上元朝,但是国家的地位,各代都能够长久;推究当中的原因,就是元朝的道德,不及中国其馀各代的道德那样高尚。从前中国民族的道德因为比外国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国到外来的蒙古人,后来蒙古人还是被中国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国到外来的满洲人,后来满洲人也是被中国人所同化。因为我们中国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此刻中国正是新旧潮流相冲突的时候,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
前几天我到乡下进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后进的一间厅堂去休息,看见右边有一个孝字,左边便一无所有,我想从前必定有一个忠字。像这些景象,我看见了的不止一次,有许多祠堂或家庙,都是一样的。不过我前天所看见的孝字,是特别的大,左边所拆去的痕迹还是很新鲜。推究那个拆去的行为,不知道是乡下人自己做的,或者是我们所驻的兵士做的。但是我从前看到许多祠堂庙宇没有驻过兵,都把忠字拆去了,由此便可见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他拆去。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民是可不可以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以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有所不惜,这便是忠。所以古人讲忠字,推到极点便是一死。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便不讲忠字,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便是大错。现在人人都说到了民国,什么道德都破坏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
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才自然可以强盛。
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对于仁爱,究竟是怎么样实行,便可以知道了。中外交通之后,一般人便以为中国人所讲的仁爱,不及外国人;因为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开办医院,来教育中国人救济中国人,都是为实行仁爱的。照这样实行一方面讲起来,仁爱的好道德,中国现在似乎远不如外国;中国所以不如的原故,不过是中国人对于仁爱没有外国人那样实行,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袛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
讲到信义,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义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在商业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袛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比方外国人和中国人订一批货,彼此不必立合同;袛要记入账簿,便算了事。但是中国人和外国人订一批货,彼此便要立很详细的合同;如果在没有律师和没有外交官的地方,外国人也有学中国人一样袛记入帐簿便算了事的,不过这种例子很少,普通都是要立合同。逢著没有立合同的时候,彼此定了货到交货的时候,如果货物的价格太贱,还要去买那一批货,自然要亏本;譬如定货的时候,那批货价订明是一万元,在交货的时候,袛值五千元,若是收受那批货,便要损失五千元;推到当初订货的时候,没有合同,中国人本来把所定的货,可以辞却不要,但是中国人为履行信用起见,宁可自己损失五千元,不情愿辞去那批货;所以外国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赞美中国人,说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得多。但是外国人在日本做生意的,和日本人订货,纵然立了合同,日本人也常不履行;譬如定货的时候,那批货订明一万元,在交货的时候,价格跌到五千元,就是原来订有合同,日本人也不要那批货,去履行合同,所以外国人常常和日本人打官司,在东亚住过很久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与日本人都做过了生意的,都赞美中国人,不赞美日本人。
至于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比方从前的高丽,名义上是中国的藩属,事实上是一个独立国家;就是在三十年以前,高丽还是独立,到了近来一二十年,高丽才失去自由。从前有一天我和一位日本朋友谈论世界问题,当时适欧战正剧,日本方参加协约国去打德国,那位日本朋友说:“他本不赞成日本去打德国,主张日本要守中立,或者参加德国来打协约国;但是因为日本和英国是同盟的,订过了国际条约的,日本因为要讲信义,履行国际条约,故不得不牺牲国家的权利,去参加协约国,和英国共同去打德国”。我就问那位日本人说:“日本和中国不是立过了马关条约吗?该条约中最要之条件不是要求高丽独立吗?为什么日本对于英国,能够牺牲国家权利去履行条约,对于中国,就不讲信义,不履行马关条约呢?对于高丽独立是日本所发起所要求,且以兵力胁迫而成的,今竟食言而肥,何信义之有呢?”?简直的说,日本对于英国,主张履行条约,对于中国,便不主张履行条约,因为英国是很强的,中国是很弱的。日本加入欧战,是怕强权不是讲信义罢!中国强了几千年而高丽犹在,日本强了不过二十年,便把高丽灭了,由此便可见日本的信义不如中国,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
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民族,袛有中国是讲和平,外国都是讲战争,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的国家。近年因为经过许多大战,残杀太大,才主张免去战争,开了好几次和平会议;像从前的海牙会议,欧战之后的华赛尔会议,金那瓦会议,华盛顿会议,最近的洛桑会议;但是这些会议中,各国人士公同去讲和平,是因为怕战争,出于勉强而然的,不是出于一般国民的天性。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之一,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
我们旧有的道德,应该恢复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我们自被满清征服了以后,四万万人睡觉,不但是道德睡觉了,连智识也睡了觉;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智识也应该唤醒他。中国有什么固有的智识呢?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智识中所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
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他放在智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我们祖宗对于这些道德上的功夫,从前虽然是做过了的;但是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后,这些智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一段话做口头禅,但是多是习而不察不求甚解莫名其妙的。正心诚意的学问是内治的功夫,是很难讲的,从前宋儒是最讲究这些功夫的,读他们的书,便可以知道他们做到了什么地步。但是说到修身、齐家、治国,那些外修的工夫,恐怕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专就外表来说,所谓修身、齐家、治国,中国人近几百年以来,都做不到;所以对于本国,便不能自治,外国人看见中国人不能治国,便要来共管。
我们为什么不能治中国呢?外国人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依我个人的眼光看,外国人从齐家一方面,或者把中国家庭看不清楚;但是从修身一方面来看,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些工夫,是很缺乏的。中国人一举一动,都欠检点,袛要和中国人来往过一次,便被他们看得很清楚。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国住过了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者是极大的哲学家像罗素那一样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国来,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于欧美,才赞美中国;普通外国人,总说中国人没有教化,是很野蛮的。推求这个原因,就是大家对于修身的工夫太缺乏;大者勿论,即一举一动,极寻常的工夫,都不讲究。譬如中国人初到美国的时候,美国人本来是平等看待,没有什么中美人的分别;后来美国大旅馆都不准中国人住,大的酒店都不许中国人去吃饭,这就是由于中国人没有自修的工夫。
我有一次在船上和一个美国船主谈话,他说:“有一位中国公使,前一次也坐这个船,在船上到处喷涕吐痰,就在这个贵重的地毡上吐痰,真是可厌”。我便问他:“你当时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我想到无法,袛好当他的面,用我自己的丝巾,把地毡上的痰擦干净便了。当我擦痰的时候,他还是不经意的样子”。像那位公使在那样贵重的地毡上都吐痰,普通中国人大都如此,由此一端,便可见中国人举动,是缺乏自修的功夫。
孔子从前说席不正不坐,由此便可见他平时修身虽一坐立之微,亦是很讲究的;到了宋儒时代,他们正心,诚意和修身的工夫,更为谨严;现在中国人便不讲究了。为什么外国的大酒店,都不许中国人去吃饭呢?有人说:“有一次一个外国大酒店,当会食的时候,男男女女非常热闹,非常文雅,济济一堂,各乐其乐;忽然有一个中国人放起屁来,于是同堂的外国人哗然哄散”。由此店主便把那位中国人逐出店外,从此以后外国大酒店就不许中国人去吃饭了。又有一次,上海有一位大商家,请外国人来宴会,他也忽然在席上放起屁来,弄到外国人的脸都变红了;他不但不检点,反站起来大拍衫裤,且对外国人说:“隘士巧士咪1[英文Excuseme的译音,意思是“对不起”。]。”这种举动,真是野蛮陋劣之极,而中国之文人学子,亦常有此鄙陋行为,实在难解。或谓有气必放,放而要响,是有益卫生,此更为恶劣之谬见,望国人切当戒之!以为修身的第一步工夫。
此外中国人每爱留长指甲,长到一寸多长,都不剪去,常以为要这样,便是很文雅。法国人也有留指甲的习惯,不过法国人留长指甲,只长到一两分,他们以为要这样,便可表示自己是不做粗工的人。中国人留长指甲,也许有这个意思,如果人人都不想做粗工,便和我们中国国民党尊重劳工的原理相违背了。再者中国人牙齿是常常很黄黑的,总不去洗刷干净,也是自修上的一大缺点。像吐痰、放屁、留长指甲、不洗牙齿,都是修身上寻常的工夫,中国人都不检点,所以我们虽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智识,外国人一遇见了便以为很野蛮,便不情愿过细来考察我们的智识。外国人一看到中国,便能够知道中国的文明,除非是大哲学家,像罗素那一样的人才能见到;否则便要在中国多住几十年,方可以知道中国几千年的旧文化。假如大家把修身的工夫做得很有条理,诚中形外,虽至一举一动之微,亦能注意,遇到外国人不以鄙陋行为而侵犯人家的自由,外国人一定是很尊重的。所以今天讲到修身,诸位新青年便应该学外国人的新文化,只要先能够修身,便可来讲齐家治国。现在各国的政治都进步了,袛有中国是退步,何以中国要退步呢?就是因为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推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修身;不知道中国从前讲修身,推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是很精微的智识,是一贯的道理,像这样很精微的智识和一贯的道理,都是中国所固有的,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智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
我们除了智识之外,还有固有的能力。现在中国人看见了外国的机器发达,科学昌明,中国人现在的能力,当然不及外国人,但是在几千年前,中国人的能力是怎么样呢?从前中国人的能力,还要比外国人大得多。外国现在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中国从前发明的。比如指南针在今日航业最发达的世界,几乎一时一刻都不能不用他。推究这种指南针的来源,还是中国人在几千年以前所发明的。如果从前的中国人没有能力,便不能发明指南针,中国人固老早有了指南针,外国人至今还是要用他,可见中国人固有的能力,还是高过外国人。其次在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东西,便是印刷术,现在外国改良的印刷机,每点钟可以印几万张报纸,推究他的来源,也是中国发明的。再其次在人类中日用的瓷器,更是中国发明的,是中国的特产,至今外国人竭力仿效,犹远不及中国瓷器的精美。近来世界战争用到无烟火药,推究无烟火药的来源,是由于有烟黑药改良而成的,那种有烟黑药也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这些重要的东西,外国今日知道利用发展他,所以他们能够有今日的强盛。
至若人类所享衣食住行的种种设备,也是我们从前发明的。譬如就饮料一项说,中国人发明茶叶,至今为世界之一大需要,文明各国皆争用之。以茶代酒,更可免了酒患,有益人类不少。讲到衣一层,外国人视为最贵重的是丝织品。现在世界上穿丝的人,一天多过一天,推究用蚕所吐的丝而为人做衣服,也是中国几千年前所发明的。讲到住一层,现在外国人建造的房屋,自然是很完全,但是造房屋的原理,和房屋中各重要部分,都是中国人发明的,譬如拱门就是以中国的发明为最早。至于走路,外国人现在所用的吊桥,便以为是极新的工程,很大的本领,但是外国人到中国内地来,走到川边西藏,看见中国人经过大山,横过大河,多有用吊桥的。他们从前没有看见中国的吊桥,以为这是外国先发明的,及看见了中国的吊桥,便把这种发明归功到中国。由此可见中国古时不是没有能力的,因为后来失去了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
但是恢复了我们固有的道德智识和能力以外,在今日的时代,还未能进中国于世界第一等的地位,像我们祖宗在从前是世界上独强一样。要想恢复到那样的地位,除了恢复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的长处,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还是要退后。我们要学外国,到底是难不难呢?中国人向来以为外国的机器是很艰难,是不容易学的;不知道外国所视为最难的,是飞上天。他们最新的发明的飞机,现在我们天天看见大沙头的飞机,天天飞上天,飞上天的技师是不是中国人呢?外国人飞上天都可以学得到,其馀的还有什么难事学不到呢?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用我们的本能,很可以学外国人的长处。外国人的长处是科学,用了两三百年的工夫,去研究发明,到了近五十年来,才算是十分进步;因为这种科学进步,所以人力巧夺天工,天然所有的物力,人工都可以做得到。
最新发明的物力是用电,从前物力的来源是用煤,由于煤便发动汽力,现在进步到用电,所以外国的科学已经由第一步进到第二步。现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计划,是要把全国机器厂所用的动力(即马达)都统一起来。因为他们全国的机器厂有几万家,各家工厂都有一个发动机,都要各自烧煤去发生动力,所以每天各厂所烧的煤和所费的人工都是很多;且因各厂用煤太多,弄到全国的铁路虽然有了几十万英里,还不敷替他们运煤之用,更没有工夫去运农产,于是各地的农产,便不能运出畅销。因为用煤有这两种的大不利,所以美国现在想做一个中央电厂,把几万家工厂用电力去统一;将来此项计划如果成功,那几万家工厂的发动机,都统一到一个总发动机,各工厂可以不必用煤和许多工人去烧火,只用一条铜线,便可以传导动力,各工厂便可以去做工。行这种方法的利益,好比现在讲堂内的几百人,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用锅炉去煮饭吃,是很麻烦的,是很浪费的;如果大家合拢起来,只用一个大锅炉去煮饭吃,就便当得多,就节省得多。现在美国正是想用电力去统一全国工厂的计划,如果中国要学外国的长处,起首便应该不必用“煤力”而用“电力”,用一个大原动力供给全国;这样学法好比是军事家迎头截击一样,如果能够迎头去学,十年之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
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著他。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我们到了今日的地位,如果还是睡觉,不去奋斗,不知道恢复国家的地位,从此以后,便要亡国灭种。现在我们知道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必可以学得比较外国还要好,所谓后来者居上。从前虽然是退后了几百年,但是现在只要几年便可以赶上。日本便是一个好榜样,日本从前的文化,是从中国学去的,比较中国低得多,但是日本近来专学欧美的文化,不过几十年便成为世界中列强之一。我看中国人的聪明才力,不亚于日本,我们此后去学欧美,比较日本还要容易。所以这十年中,便是我们的生死关头!如果我们醒了,像日本人一样,大家是提心吊胆,去恢复民族的地位,在十年之内,就可以把外国的政治经济和人口增加的种种压迫和种种祸害,都一齐消灭。
日本学欧美不过几十年,便成世界列强之一,但是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领土比日本大三十倍,富源更是比日本多,如果中国学到日本,就要变成十个强国。现在世界之中英美法日意大利等,不过五大强国,以后德俄恢复起来,也不过六七个强国,如果中国能够学到日本,只要用一国便变成十个强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便可以恢复到头一个地位!
但是中国到了头一个地位,是怎么样做法呢?中国古时常讲“济弱扶倾”,因为中国在政治文化正统思想上有了这个好政策;所以强了几千年,安南缅甸高丽暹罗那些小国,还能够保持独立。现在欧风东渐,安南便被法国灭了,缅甸被英国灭了,高丽被日本灭了。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么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没有大利,便有大害。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我们今日在没有发达之先,立定“济弱扶倾”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都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
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诸君都是四万万人的一份子,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这便是我们民族主义的真精神!
附录 【吴钩】《宋朝的小学生、中学生与大学生究竟上什么课程?》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初六日癸卯
耶稣2019年11月2日
宋代的学校分为大学、小学,没有中学之称。大学是太学等高等教育,相当于今天的大学阶段;小学是基础教育,又叫蒙学,启蒙教育的意思,相当于今天的小学;不过,宋朝各州郡设立的州学,实际上相当于今天的中学。
宋朝的蒙学是比较发达的,我们来看看宋朝人的描述:南宋杭州,“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这里的宗学、京学、县学是官学,即公立学校,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是私学,即民办学校、私立学校。
不独都城设有官学、私学,宋政府在各州县都建设了官学,包括小学。相比之下,私学的数目更多,比如在福建莆田,“十室九书堂”;在南剑州,“五步一塾,十步一庠”;在四川眉州,“凡一成之聚,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奠,士子私讲礼焉,名之曰乡校”。这里的“书堂”、“塾”、“庠”、“乡校”,都是民间兴办的私立小学,尽管宋人说得有些夸张,但宋朝私学之盛,可见一斑。甚至在偏远乡村,也有读书人,一位宋朝诗人写道:“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宋朝农村的孩子读书,一般是在十月份入学,叫做“冬学”。
宋朝的小学生平日要学习什么课程呢?朱熹编写过一份《童蒙须知》,说:“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也就是说,宋朝小学的教学内容,包括日常礼仪、生活习惯、基础文化知识与技能等,其中基础文化知识与技能的课程包括常用字读写、诗文阅读与创作(相当于语文课)、历史课、名物课(相当于自然课)、思想品德课,等等。
宋朝士大夫编写了大量蒙学教材,如朱熹编有六卷《小学》,吕祖谦编有《少仪外传》,黄继善编有《史学提纲》,方逢辰编有《名物蒙求》。影响最深广的宋朝蒙学教材,当属《三字经》与《百家姓》,它们与《千字文》合称“三百千”,是传统蒙学的经典教材。
《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人王应麟,清代学者评价说:“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言简意长,词明理晰,淹贯三才,出入经史,诚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也。”
《百家姓》的作者则是北宋初浙江的一名小民,姓名已佚失。因为是宋初浙江人所著,“赵钱孙李”四姓才会排在百家姓之首——赵是宋朝国姓,钱是当时钱塘国王之钱,孙是钱塘国王正妃之姓,李是后唐国主之姓。
除了《三字经》、《百家姓》,宋朝士大夫还辑录了《千家诗》,也是影响深远的蒙学教材。在宋朝之后的几百年里,传统中国最常用、最重要的蒙学教材,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可谓遗泽百世。
再来说说宋朝的州学与太学的课程。
宋代地方的州县学校也设置了科学课程,胡瑗主持湖州州学时,便将州学分为“经义”、“治事”两斋,其中“治事”斋开设治民、讲武、堰水和算历四项课程,要求学生“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宋代的书院也有科学课程,一生都致力于书院建设的朱熹主张:“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
宋朝政府并没有像明清统治者那样将科技发明视为“奇技淫巧”,加以禁绝;恰恰相反,朝廷常常对出色的科技发明者给予奖励,如冯继升改良了火药法,朝廷赐衣物束帛。在科技领域有突出才能的人通常会被列入“奇才异行”名录,可以直接选拔进政府机构。政府还有意识培养科技人才,在中央一级设立了多种专科学校,包括医学院、算学(数学)院、天文历法学校、武学院等,隶属于国子监。又实行奖学金制度,如医学院学生成绩为上等者,每月给钱十五贯,中等者给钱十贯,下等者给钱五贯。
我们要是以为古代的国子监、州县学、书院教授的仅仅是儒家经义,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想象。
宋代太学(相当于国立大学)的教学制度也堪称先进。经过王安石的改革,宋朝太学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三舍制”,学生被划分为外舍生、内舍生与上舍生三舍(相当于分为三个年级),每舍设若干斋(相当于班级),采用积分制,即学生的学习成绩量化为学分,成绩优秀的外舍生可升入内舍;内舍生成绩优异者,可升入上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将学生成绩量化计分、并按积分升等的教育制度。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宋代时,形成一座高峰,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应该说,宋朝对科技教育的重视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附录【吴钩】《宋朝的大学:不仅仅是太学》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赐稿
节选自 吴钩新书《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六月廿八日庚辰
耶稣2022年7月26日
宋朝的太学,为全国最高学府,我们不妨称之为宋代的“大学”。不过宋朝太学仅仅是国子监直辖的几所国立学校之一。太学之外,国子监还辖有多所学校:国子学、四门学、小学、辟雍。
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是北宋国子监下辖的几个专科学校。我记得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袁伟时教授曾说过:“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把数学、逻辑、法律等学科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熟读儒家经典成为主要上升渠道,导致知识阶层视野狭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但你只要略了解宋代的专科教育,便会知道袁教授所言过于偏颇,不合史实。
来看看宋朝的国子监设立了哪些专科学校——
1、律学,相当于法学院。北宋立国之初便置律学博士,传授法律。至熙宁六年(1073),于国子监下设律学,分“断案”、“律令”两个专业,断案专业主修刑名之学与案例试断;律令专业主修法理大义。律学所需的古今刑书,可向朝廷申请配备;朝廷颁布的法令,也需要关送律学。每月,律学会举行三次私试、一次公试。成绩优秀的律学生毕业后可赴吏部授官。兼修律学的太学生,在律学公试中获得第一等的成绩,可计入学分,相当于在太学私试中得第二等。
2、算学,相当于数学与天文学院,崇宁兴学期间设立,“生员以二百一十人为额,许命官及庶人为之”,入读的学生以天文、历法、算术、三式法(指卜筮之法)为必修课,再选修一门文化课,如《论语》、《孟子》,其“公私试、三舍法略如太学”,上舍的优秀毕业生可以授官。
3、书学,相当于文字学与书法学院,学生练习篆、隶、草三种字体,主修《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五书,兼通《论语》、《孟子》之义。公私试、三舍法同算学,只是毕业生所授官职“差降一等”。
4、画学,相当于美术学院,学生主要训练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题材的绘画,并学习《说文》、《尔雅》、《方言》、《释名》,士子出身的学生要求兼修两门文化课,杂流出身的人要求兼修一门文化课。考试主要为“试画”,“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并委托太学“试经义”。优秀毕业生授官待遇如书学。
5、武学,相当于军事与武术学校,学生主修武艺、兵法,考试时,先试军机策论,再试骑射之术。武学生毕业后可获授巡检、监押等职务。
6、医学,相当于医学院,初隶属于太常寺,崇宁兴学期间,考虑到“所有医工未有奖进之法,盖其流品不高,士人所耻,故无高识清流习尚其事。今欲别置医学,教养上医”,遂另建医学院,改隶国子监。
北宋医学分“方脉科”、“针科”、“疡科”三个专业。方脉科有点接近今人所说的内科,其学生主修大方脉、小方脉、风科等专业课,兼习王氏《脉经》、张仲景《伤寒论》;针科类似于今天的针炙科加五官科,其学生主修大针炙、口齿、咽喉、眼耳等专业课,兼习《针炙经》、《龙本论》;疡科接近今天的外科,其学生通习疮肿、伤折、金疮等专业课,兼习《针炙经》、《千金翼方》。
除了专业课,还有公共课,方脉科、针科、疡科三个专业的学生都需要学习《黄帝素问》、《难经》、《巢氏病源》、《补本草》、《千金方》。此外还有实习课:太医局在“近城置药园种药,其医学生员,亦当诣园辨识诸药”。
医学亦仿太学三舍法,“立上舍四十人,内舍六十人,外舍二百人”。外舍生升内舍生主要看私试与公试的成绩。内舍生升上舍生,以及上舍生能不能毕业,则不但看考试成绩,还要看“医治比校”,即行医实习的积分。
“医治比校”是这么设计的:给医学内舍生、上舍生每人发一本“印历”,定期派往太学、武学、律学、算学、艺学(即书学与画学)实习行医,医治患病的学生。诊治时候,必须在“印历”上“书其所诊疾状”,送回医学院盖章。然后按疾病的疗程,如实登记治疗结果:“愈或失”,并报医学院核实盖章。年中进行“比校”,合格的成绩分为三等:100%的治愈率为上等,给10个学分;90%的治愈率为中等,给9个学分;80%的治愈率为下,给8个学分。
在“医治比校”中获得10个学分的医学内舍生,可以申请试上舍,只要在考试中得到“平”的成绩,便能升舍;如果是上舍生获得10个学分,则可毕业授官,“听保明推恩”,一般是“选充尚药局医师”,或者安排为国子监及诸州府医学的教授;得到8个或9个学分的学生,则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才可以升补或毕业;只得到7个学分的学生,降舍,即从上舍降至内舍,或从内舍降至外舍;5个学分以下的学生,“屏出学”,即勒令退学。
说到这里,想起了一句宋诗:“太学诸斋拣秀才,出门何处是金台?”诗中的秀才,非指一般的读书人,也非指科举制度中的生员(明清时期,“秀才”方有这两个含义),而是指优秀的才俊之士;金台,为国家延揽士人的象征性建筑。太学设诸斋、分三舍,意在培养与遴选优秀的人才。太学之外,又置医学、律学、算学等专科学校,当然也是为了培养杰出的专业人才。宋朝才俊辈出,人文与科技成就都足称鼎盛,与其发达的教育制度是分不开的。
最后,顺便一说:唐宋时期的国子监是一个教育行政机构,下辖多所学校,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元明清时期的国子监只是一所国立学校,与从前的国子学相类。因此,虽然自唐至清均设有国子监祭酒一职,但唐宋时期的国子监祭酒是教育部长,元明清时期的国子监祭酒只是一所国立学校的校长而已。
附录【钱穆】《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
要谈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首先应该提到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精神和理想。此项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精神和理想,创始于三千年前的周公,完成于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此项教育的主要意义,并不专为传授知识,更不专为训练职业,亦不专为幼年、青年乃至中年以下人而设。此项教育的主要对象,乃为全社会,亦可说为全人类,不论幼年、青年、中年、老年,不论男女,不论任何职业,亦不论种族分别,都包括在此项教育精神与教育理想之内。
中国传统教育的宗教精神
在中国的文化体系里,没有创造出宗教,直到魏、晋、南北朝以后,始有印度佛教传入,隋、唐时代,乃有伊斯兰教、耶教等相继东来。中国社会并不排拒外来宗教,而佛教在中国社会上,尤拥有广大信徒。亦可说,佛教虽创始于印度,但其终极完成则在中国。但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佛教仍不占重要地位。最占重要地位者,仍为孔子之儒教。
孔子儒教,不成为一项宗教,而实赋有极深厚的宗教情感与宗教精神。如耶教、佛教等,其教义都不牵涉到实际政治,但孔子儒教,则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终极理想,故儒教鼓励人从政。又如耶教、佛教等,其信徒都超然在一般社会之上来从事其传教工作。但孔子儒家,其信徒都没入在一般社会中,在下则宏扬师道,在上则服务政治。只求淑世,不求出世。故儒教信徒,并不如一般宗教之另有团体,另成组织。
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教育即负起了其它民族所有宗教的责任。儒家教义,主要在教人如何为人。亦可说儒教乃是一种人道教,或说是一种人文教,只要是一个人,都该受此教。不论男女老幼,不能自外。不论任何知识、任何职业,都该奉此教义为中心,向此教义为归宿。在其教义中,如孝、弟、忠、恕,如仁、义、礼、智,都是为人条件,应为人人所服膺而遵守。
中国的这一套传统教育,既可代替宗教功能,但亦并不反对外来宗教之传入。因在中国人观念里,我既能服膺遵守一套人生正道,在我身后,若果有上帝诸神,主张正道,则我亦自有上天堂进极乐国的资格。别人信奉宗教,只要其在现实社会中不为非作歹,我以与人为善之心,自也不必加以争辩与反对。因此在中国文化体系中,虽不创兴宗教,却可涵容外来宗教,兼收并包,不起冲突。
中国儒家人品观:人人皆可为尧舜
在中国儒家教义中,有一种人品观,把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作评判标准,来把人分作几种品类。即如自然物乃至人造物,亦同样为他们品第高下。无生物中如石与玉,一则品价高,一则品价低。有生物中,如飞禽中之凰凤,走兽中之麒麟。水生动物中,如龙与龟,树木中如松、柏,如梅、兰、竹、菊。人造物中,如远古传下的钟、鼎、彝器,以及一应精美高贵的艺术品,在中国人心目中,皆有甚高评价。物如此,人亦然。故中国人常连称人物,亦称人品。物有品,人亦有品。天地生物,应该是一视同仁的。但人自该有人道作标准来赞助天道,故曰:“赞天地之化育”,中国人贵能天人合德,以人来合天。不主以人蔑天,亦不主以天蔑人。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有其天道观,亦有其人道观。有其自然观,亦有其人文观。两者贵能相得而益彰,不贵专走一偏。
中国人的人品观中,主要有君子与小人之别。君者,群也。人须在大群中做人,不专顾一已之私,并兼顾大群之公,此等人乃曰“君子”。若其人,心胸小,眼光狭,专为小己个人之私图谋,不计及大群公众利益,此等人则曰“小人”。在班固《汉书》的《古今人表》里,把从来历史人物分成九等。先分上、中、下三等,又在每等中各分上、中、下,于是有上上至下下共九等。历史上做皇帝,大富大贵,而列人下等中,乃至列入下下等的尽不少。上上等是圣人,上中等是仁人,上下等是智人。中国古人以仁智兼尽为圣人,故此三等,实是一等。最下下等是愚人。可见中国人观念,人品分别,乃由其智愚来。若使其知识开明,能知人道所贵,自能做成一上品人。因其知识闭塞,不知人道所贵,专为己私,乃成一下品人。故曰:“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此则须待有教育。苟能受教育,实践人道所贵,则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类的理想,乃使人人同为上等人,人人同为圣人,此是中国人的平等观。
中国人言人品,又常言品性品德。人之分品,乃从其人之德性分。天命之谓性,人性本由天赋,但要人能受教育,能知修养,能把此天赋之性,实践自得,确有之己,始谓之德。德只从天性来。天性相同,人人具有。人之与人,同类则皆相似,故人人皆能为尧舜。而且尧舜尚在上古时代,那时教育不发达,尧舜能成为第一等人,我们生在教育发达之后世,只要教育得其道,岂不使人人皆可为尧舜。若使全世界人类,同受此等教育熏陶,人人同得为第一等之圣人。到那时,便是中国人理想中所谓大同太平之境。到此则尘世即是天堂。人死后的天堂且不论,而现实的人世,也可以是天堂了。故说中国传统教育的理想与精神,是有他一番极深厚的宗教情趣与宗教信仰的。
中国人传统教育的理想与精神,既然注重在人之德性上,要从先天自然天赋之性,来达成其后天人道文化之德,因此中国人的思想,尤其是儒家,便特别注意到人性问题上来。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性由天赋,人若能知得自己的性,便可由此知得天。但人要知得自己的性,该能把自己的那一颗心,从其各方面获得一尽量完满的发挥,那才能知得自己的性。人心皆知饮食男女,饮食男女亦是人之性,但人的心不该全在饮食男女上,人的性亦不只仅是饮食男女。人若专在饮食男女上留意用心,此即孟子所谓养其小体为小人。
中国儒家人品观:文化多元
人的生命,有小体,有大体。推极而言,古今将来,全世界人类生命,乃是此生命之大全体。每一人之短暂生命,乃是此生命之最小体。但人类生命大全体,亦由每一人之生命小体会通积累而来。不应由大体抹杀了小体,亦不应由小体忽忘了大体。
儒家教义,乃从每一人与生俱来各自固有之良知良能,亦可说是其本能,此即自然先天之性。由此为本,根据人类生命大全体之终极理想,来尽量发展此自然先天性,使达于其最高可能,此即人文后天之性。使自然先天,化成人文后天。使人文后天,完成自然先天。乃始是尽性知天。若把自然先天单称性,则人文后天应称德。性须成德,德须承性。性属天,人人所同。德属人,可以人人有异。甚则有大人小人之别。有各色人品,有各类文化。
世界诸大宗教,都不免有尊天抑人之嫌。惟有中国儒家教义,主张由人合天。而在人群中,看重每一小己个人。由每一小己个人来尽性成德,由此人道来上合于天道。没有人道,则天道不完成。没有每一小己个人之道,则人道亦不完成。近代人喜言个人自由,实则中国儒家教义,主张尽性成德,乃是每一人之最高最大的自由。由此每一人之最高最大的自由,来达成全人类最高最大的平等,即是人人皆为上上第一等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儒家教义由此理想来教导人类,此为对人类最高最大之博爱,此即孔子之所谓仁。
中国儒家教育观:高人品高人格,方能为人师
中国儒家此一种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既不全注重在知识传授与职业训练上,更不注重在服从法令与追随风气上,其所重者,乃在担任教育工作之师道上,乃在堪任师道之人品人格上。故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若要一人来传授一部经书,其人易得。若要一人来指导人为人之道,其人难求。因其人必先自己懂得实践了为人之道,乃能来指导人。必先自己能尽性成德,乃能教人尽性成德,《中庸》上说:“尽己之性,乃能尽人之性。”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因其人品人格最高,乃能胜任为人师之道,教人亦能各自尽性成德,提高其各自之人品人格。
韩愈《师说》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其实此三事只是一事。人各有业,但不能离道以为业。如为人君,尽君道。为人臣,尽臣道。政治家有政治家之道。中国人常说信义通商,商业家亦有商业家之道。社会各业,必专而分,但人生大道,则必通而合。然人事复杂,利害分歧,每一专门分业,要来共通合成一人生大道,其间必遇许多问题,使人迷惑难解,则贵有人来解其惑。所以传道者必当授之业而解其惑。而授业解惑,亦即是传道。
中国儒家教育观:道义远重于职业
孔子门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子夏列文学科,孔子教之曰:“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则治文学科者,仍必上通于德行。子路长治军,冉有擅理财,公西华熟娴外交礼节,各就其才性所近,可以各专一业。但冉有为季孙氏家宰,为之理财,使季孙氏富于周公,此已违背了政治大道。孔子告其门人曰:“冉有非吾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但季孙氏也只能用冉有代他理财,若要用冉有来帮他弑君,冉有也不为。所以冉有还得算是孔门之徒,还得列于政事科。至于德行一科,尤是孔门之最高科。如颜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学了满身本领,若使违离于道,宁肯藏而不用。可见在孔门教义中,道义远重于职业。
宋代大教育家胡瑗,他教人分经义、治事两斋。经义讲求人生大道,治事则各就才性所近,各治一事,又兼治一事。如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从来中国学校,亦重专业教育,如天文、历法、刑律、医药等。近代教育上,有专家与通才之争。其实成才则就其性之所近,宜于专而分。中国传统教育,也不提倡通才,所提倡者,乃是通德通识。故曰:“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有了通德通识,乃为通儒通人。人必然是一人。各业皆由人担任。如政治、如商业,皆须由人担任。其人则必具通德,此指人人共通当有的,亦称达德。担任这一业,也须懂得这一业在人生大道共同立场上的地位和意义,此谓之通识。通德属于仁,通识属于智。其人具有通德通识,乃为上品人,称大器,能成大业,斯为大人。若其人不具通德通识,只是小器,营小事,为下品人。
中国儒家人品观:雅士即君子
中国人辨别人品,又有雅俗之分。俗有两种,一是空间之俗,一是时间之俗。限于地域,在某一区的风气习俗之内,转换到别一区,便不能相通,限于时代,在某一期的风气习俗之内,转换到另一期,又复不能相通。此谓小人俗人。大雅君子,不为时限,不为地限,到处相通。中国在西周初期,列国分疆,即提倡雅言雅乐,遂造成了中国民族更进一步之大统一。此后中国的文学艺术,无不力求雅化。应不为地域所限,并亦不为时代所限。文学艺术如此其它人文大道皆然。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此项大道,其实只在一个小己个人的身上,此一人便成为君子。但君子之道,并不要异于人,乃要通于人。抑且要通一大群一般人。故曰征诸庶民,要能在庶民身上求证。考诸三世,是求证于历史。建诸天地,是求证于大自然。质诸鬼神,是求证于精神界。此项大道,惟遇圣人,可获其首肯与心印。圣人不易遇,故将百世以俟。但此一君子,其实亦可谓只是一雅人。雅即通,要能旁通四海,上下通千古,乃为大雅之极。故既是君子,则必是一雅人。既是雅人,亦必是一君子。但没有俗的君子,亦没有雅的小人。只中国人称君子,都指其日常人生一切实务言。而中国人称雅人,则每指有关文学艺术的生活方面而言。故君子小人之分,尤重于雅俗之分。
中国传统教育,亦可谓只要教人为君子不为小人,教人为雅人不为俗人。说来平易近人,但其中寓有最高真理,非具最高信仰,则不易到达其最高境界。中国传统教育,极富宗教精神,而复与宗教不相同,其要端即在此
中国传统教育,因寓有上述精神,故中国人重视教育,往往不重在学校与其所开设之课程,而更重在师资人选。在中国历史上,自汉以下,历代皆有国立太学。每一地方行政单位,亦各设有学校。乡村亦到处有私塾小学。但一般最重视者,乃在私家讲学。战国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竞起,此姑不论。在两汉时代,在野有一名师,学徒不远千里,四面凑集,各立精庐,登门求教,前后可得数千人。亦有人遍历中国,到处访问各地名师。下至宋、元、明三代,书院讲学,更是如此。所以在中国传统教育上。更主要者,乃是一种私门教育、自由教育。其物件,则为一种社会教育与成人教育。孔子死后,不闻有人在曲阜兴建一学校继续讲学。朱子死后,不闻有人在武夷、五曲,在建阳、考亭兴建一学校继续讲学。更如王阳明,只在他随处的衙门内讲学,连书院也没有。中国传统教育之主要精神,尤重在人与人间之传道。既没有如各大宗教之有教会组织,又不凭借固定的学校场所。只一名师平地拔起,四方云集。不拘形式地进行其教育事业,此却是中国传统教育一特色。
唐代佛教中禅宗崛起,他们自建禅寺,与一般佛寺不同。可以没有佛殿,可以不开讲一部佛门经典。但有了一祖师,四方僧徒,云集而至。一所大丛林,可以有数千行脚僧,此来彼往,质疑问难。一旦自成祖师,却又另自开山,传授僧徒。禅宗乃是佛教中之最为中国化者,其传教精神,亦复是中国化。
中国儒家精神与理想:人生不能只是功利的
近代的世界,宗教势力,逐步衰退。西方现代教育,最先本亦由教会发动,此刻教会势力亦退出了学校。教育全成为传播知识与训练职业。只有中小学,还有一些教导人成为一国公民的教育意义外,全与教导人为人之道的这一大宗旨,脱了节。整个世界,只见分裂,不见调和。各大宗教,已是一大分裂。在同一宗教下,又有宗派分裂。民族与国家,各自分裂。人的本身,亦为职业观念所分裂。如宗教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法律家、财政经济家、企业资本家等,每一职业,在其知识与技能方面,有杰出表现杰出成就者,均目为一家。此外芸芸大众,则成无产阶级与雇用人员。好像不为由人生大道而有职业,乃是为职业而始有人生。全人生只成为功利的、唯物的。
庄子说:“道术将为天下裂。”今天世界的道术,则全为人人各自营生与牟利,于是职业分裂。德性一观念,似乎极少人注意。职业为上,德性为下,德性亦随职业而分裂。从事教育工作者,亦被视为一职业。为人师者,亦以知识技能分高下,非犯法,德性在所不论。科学被视为各项知识技能中之最高者。《中庸》说:“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大学》说“格物”,其最后目标乃为国治而天下平。朱子说:“格物穷理”,其所穷之理,乃是吾心之全体大用,与夫国治天下平之人生大道。近代科学,只穷物理,却忽略了人道,即人生之理。原子弹、核武器,并不能治国平天下。送人上月球,也非当前治国平天下所需,科学教育只重智,不重仁。在《汉书》的《古今人表》里,最高只当列第三等,上面还有上上、上中两等,近代人全不理会。中国传统教育之特殊理想与特殊精神,在现实世界之情势下,实有再为提倡之必要。
中国传统教育观:人皆有向上心,需要君子做榜样
而且中国传统教育理想,最重师道。但师道也有另一解法。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子贡亦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可见人人可以为人师,而且亦可为圣人师。中国人之重师道,其实同时即是重人道。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柳下惠并不从事教育工作,但百世之下闻其风而兴起,故说为百世师。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所以儒家教义论教育,脱略了形式化。只要是一君子,同时即是一师。社会上只要有一君子,他人即望风而起。又说:“君子之教,如时雨化之。”只要一阵雨,万物皆以生以化。人同样是一人,人之德性相同,人皆有向上心。只要一人向上,他人皆跟着向上。中国古人因对人性具此信仰,因此遂发展出像上述的那一套传统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精神。
不要怕违逆了时代,不要怕少数,不要怕无凭借,不要计及权势与力量。单凭小己个人,只要道在我身,可以默默地主宰着人类命运。否世可以转泰,剥运可以转复。其主要的枢纽,即在那一种无形的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上。此可以把中国全部历史为证。远从周公以来三千年,远从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年,其间历经不少衰世乱世,中国民族屡仆屡起,只是这一个传统直到于今,还将赖这一个传统复兴于后。这是人类全体生命命脉之所在。中国人称之曰:“道”。“教统”即在此“道统”上,“政统”亦应在此“道统”上。全世界各时代、各民族、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体系、各大教育组织,亦莫不合于此者盛而兴,离于此者衰而亡。而其主要动机,则掌握在每一小已个人身上。明末遗民顾亭林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内涵意义亦在此。
由于中国传统而发展成为东方各民族的文化体系,韩国人的历史,至少亦该远溯到三千年以上。即根据韩国史,我想亦可证成我上面之所述。我中、韩两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身负教育责任的,应该大家奋起,振作此传统精神,发扬此传统理想。从教育岗位上,来为两民族前途,为全世界人类前途,尽其最高可能之贡献。
认识传统就是认识自己
我要特别说明,我很喜欢这“传统”二字,因这传统二字,特别重要。但要认识传统,其事不易。好像有些时候,我们要认识别人反而易,要认识自己反而难。而且要认识我们东方人的传统,要比认识西方人的传统其事难。如中国有四千年、五千年以上的传统,韩国有三千年以上的传统,日本有二千年以上的传统。西方如法国、英国,只有一千年传统,美国只有两百到四百年传统,苏维埃没有一百年传统。
教育的第一任务,便是要这一国家这一民族里面的每一分子,都能来认识他们自己的传统。正像教一个人都要能认识他自己。连自己都不认识,其它便都不必说了。
对西方教育不能奉行“拿来主义”
今天,我们东方人的教育,第一大错误,是在一意模仿西方,抄袭西方。不知道每一国家每一民族的教育,必该有自己的一套。如韩国人的教育,必该教大家如何做一韩国人,来建立起韩国自己的新国家,发扬韩国自己的新文化,创造出韩国此下的新历史。这一个莫大的新任务,便该由韩国人自己的教育来负担。要负担起此一任务,首先要韩国人各自认识自己,尊重自己,一切以自己为中心,一切以自己为归宿。
但这不是说要我们故步自封,闭关自守。也不是要我们不懂得看重别人,不懂得学别人长处来补自己短处。但此种种应有一限度。切不可为要学别人而遗忘了自己,更不可为要学别人而先破灭了自己。今天,我们东方人便有这样的趋势,亟待我们自己来改进。
附录【钱穆】《改革中等教育议》
鄙人前撰《改革大学制度议》,粗陈涯略,间滋误会。或疑鄙意菲薄实科与专业,此在原文申说已明,无烦辩解。或疑鄙意提倡通学,有减低大学程度之嫌,则由时贤夙习,尊专业,蔑通学,故云尔。鄙文特主教育旨趣转换一方向,并与程度高下无涉。昔人论学,每言博约。博不即是通,必博而有统类而能归于约之谓通;专不即是约,约如程不识将兵,有部勒约束,又如满地散钱,以一贯串之。故约以博为本。而今之专业,则偏寻孤搜,或不待于博。就此言之,倡导通学,毋宁是提高程度也。或主中学教育应主通,大学教育应主专,此亦不了通学难企,误谓略具常识即为通,是又浅之乎视通矣。且学校教育与私人学问,判属两事。私人学问当各就性业,毕生从事;学校教育则为青年壮年人树立一共同基础,律可由此上进。今谓中学修其通,大学务其专,是欲以学校教育包办私人学问,代大匠斫,希不伤手。时论既多主提高中学程度以为大学专精之阶梯,爰草此文,再献刍荛。
各阶段之教育,本各有独特之任务,中学校非专为投考大学之预备而设。目前各中学程度,难免低落,此乃一时现象。若就民十七至民二十七此十年间江浙平津一带而论,则中学校课程,已不嫌其过松,而嫌其过紧。专就学业知识论,似乎所望于中学生者,已嫌其过高,而不嫌其过浅。中等教育本与大学有别。知识学业之传授,并不当占最高之地位。青年期之教育,大要言之,应以锻炼体魄,陶冶意志,培养情操,开发智能为主,而传授知识与技能次之。今日国内有一至可悲观之现象,厥为知识分子体魄与精力之不够标格。一二十岁上下之中学毕业生,已渐具书生气,精神意识已嫌早熟。至大学毕业,年未壮立,而少年英锐之气已销磨殆尽,非老成,即颓唐。社会政军商学各界领袖,大体年龄,较之欧美各国,比数相差几有二十至三十年之巨。中国各界主持活动之强固中心人物,率在四十前后,而欧美各邦,则六十七十不为老。大抵中国人一过三十,便无勇猛精进可言。一过五十,便无强立不返可言。精神意气早熟早衰,社会活力日以沦浙。倘更不于当前青年教育加意矫挽,国族前途,复何期望?
更论中国知识分子之毕生生活,大体自家庭入学校,自学校入社会,而此社会又大体以都市为限。莫非一温暖狭隘之境,不舍在花房中玻璃阳光下所煦育之一种盆景花卉也。其自少而壮,自壮而老,常缠绵于闺房之内,流连于城市之间。濈濈湿湿,蚁附纳集,既以丧其迈往之韵,复以研其敦庞之质。深山穷谷,惊浪骇涛,心魂既所不接,神情为之噩胎。筋骨柔脆,意兴卑近。当其在学校,非不言卫生,而卫生特享受之别名。非不言运动,而运动仅游戏之余事。其体魄之完固,精力之弥满,姑勿与并世欧美相较,回视百年前吾济所最鄙视之八股时代,盖犹有逊色焉。彼时一秀才,赴乡会试,三年一度,以交通之不便,近者数百里,远者数千里,经月累时,犹得以跋涉山川,冒历风霜,识天地之高厚,亲民物之繁变。其所以强身体而壮精神之道,有非今日学校青年所能梦想。今则掩目于书本文字之中,放胆于朋偶罄咳之侧,体魄衰而精力糜,意志不坚强,情操不高洁,智能不开敏,而矻矻焉唯知从事于知识技能之传习,造诣有限,运用无力,根本已拨,妄希花果,亦多见其不知务矣。
窃谓今日中学教育,当痛惩旧病,一变往昔偏重书本之积染,而首先加意及于青年之体魄与精力。当尽量减少讲堂自修室图书馆工作时间,而积极领导青年为户外之活动。自操场进至于田野,自田野益进至于山林,常使与自然界清新空气接触。自然启示之伟大,其为效较之书本言说,什百倍徒,未可衡量。昔德人于前次大战失败后,即主以山林自然生活恢复其青年之内心活力。吾国近百年来,全国上下,麻醉于婴粟,沉酣于麻雀,精神意趣,束缚于门庭廖邑之间。毒雾弥漫,未有所廓清。非大加荡涤,振奋无由。当使学校一切田野化、山林化,使青年一入学校,恍然于一种新生命新境界之降临。庶足以扫除国人宴安于闺门迷恋于都市之沉冗,而后身体精神知识事业始有可商。
夫教育精神,贵能因时设施,非有成局定格可以永遵勿渝也。今国民党人常言忠实同志,此言最堪味。今国人所缺,正在忠实,而所鹜则为聪明。聪明日增,忠实日减。聪明即闺房城市之习,忠实则田野山林之气。抑聪明者尚知,忠实者尚行。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深感时弊,而倡知难行易之教。其用意在励国人之起而行,非奖国人之坐而知。乃今国人群相曲解,谓唯其知难,故当勉于求知。不知尊所闻则高明矣,行所知则广大矣。一国事业,知者居其一,行者居其百。今日国人大病,不在知之不足,而在行之无实。国家社会各方面所要之人才,非患其不聪明,而患其不忠实。非患其无知,而患其不行。今日之病,非白痴,非狂惑,乃瘫痪之与萎缩也。而今日国家教育,姑以最好评语加之,则一种彻头彻尾之尚知教育也。此正如以水救水,以火救火,其何能济?
抑又有进者。知贵乎个别之钻研,行贵乎共同之协调。故务知者其群涣,励行者其体凝。务知,故各以空言争领导;励行,故互以实践期成绩。吾国自民四五提倡新文化运动以来,承学之士,莫不曰自由,曰解放。以个性伸展为旗帜,目礼教为吃人之工具。以大群为小我之桎梏,以冲决网罗打破枷锁为斗士之光辉。而流弊所届,特立孤诣之士未见其多,泛驾逸轨之象则层出无已。今日对症发药,固当裁抑小我,奖进群育。纳之轨物,宏以大道矣。
然尚知尚行,特教育精神畸轻畸重之间,非谓其截然划然如鸿沟之不可逾越也。以旧教育拟之,尚知乃诗书之教,尚行则礼乐之教也。儒者谓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以今日学校课程言,体操唱歌即犹礼乐。衡以儒家理论,此两科当为学校教育之最高科目。日日必修,不可或缺。师生并习,无分上下。大抵初级中学应以乐为主而礼副之,高级中学则以礼为主而乐副之。初级唱歌,宜多制发扬蹈厉之辞,继以宏大和平之旨。以大群合唱为主,以舞蹈进行为助。务求活泼动荡,开拓其情趣,畅悦其胸襟。而又辅之以晨夕之劳作,健身之游戏,以及郊外之远足。至高中则以严格之军事训练与大规模之山林眺览夹辅并进,而以竞技运动与庄严肃穆之歌曲辅之。其他如童子军青年营等训练,皆当切实重视,不得目为课业余暇之消遣与点缀。凡学校师生生活,皆当以礼乐为中心,以锻炼体魄,陶冶意志,培养情操,开发智慧为目的。而知识技能之传习,则降而次之。孔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子路谓“何必读书,然后为学”,皆此意也。
或疑若是则学业将有益降愈下之弊。不知苟其人体魄完固,精神充健,意志定而情趣卓,则智慧自开敏,知识技能虽粗引其绪,他日置身社会,自能得路寻向上去。孔子所谓吾见其进,未见其止也。苟既体弱而神茶,志摇而情卑,智慧昏惑,不得安宁,而徒皇皇汲汲于知识之灌输,技能之修习,今日学校青年之仿徨歧途,烦闷苦恼,激而横溃,疲而半废,前车之覆,正复可鉴。抑学校课程,果能改弦易辙,则别自有取精用宏事半功倍之道。程度之提高,不在于繁其课目,多其钟点,而在乎门类与内容之精选及教法之严格。窃谓今日学校课程,以别择不精,滥杂铺张,而浪费精力者,居三之一。以教法不严,鲁莽灭裂,而涂塞聪明者,又居三之一。若能删其芜秽,抉其蓄华,专力并赴,则课程虽简,而学业自进。合之上文所论,正可收相得益彰之效。
尝试追求今日学校课程病根,盖亦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则高唱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而结果则支离破碎,漫无准绳。一则提倡科学教育而未得其方,大学专门化之风气,浸寻波及于中学。一切课目,皆趋于形式僵化,未能提其精英,活泼运用。前者之弊,其著在文科。后者之弊,其著在理科。一则古今中外,浅深雅俗,樊然杂陈,如百袖之衣,天吴紫凤,破布败絮,裙披拚凑,陆离光怪,而不问其何以被于体。一则声光热力动植生矿,上自天文,下至地质,山珍海错,食前方丈,而不问其何以纳诸胃。前者病在驳而不纯,后者病在积而不化。一则沙石俱下,无益营卫。一则酿肥太过,徒增郁闷。今日中学课程之改进,唯有二道:曰精,曰简。庶使学者精力充沛,神智自生。否则买菜求多,学海深广,青年力弱,终有没溺之患。
又近制中学分高初两级,课程多一周环。初中学龄仅当十二三岁,即须离家外宿。学校既护育难周,稚年身心,受损匪细。谓宜仍旧贯,后期小学增一年,而高初中并合为五年制。又宜多设各项补习学校、职业学校、专修学校等,与普通中学并行,一如大学之例。
上之所陈,颇多乖背时风。如课程之改订,师资之培养,皆非仓促可希。苟非其人,虽有良法,亦莫所施。徒更规章,转滋扰动。唯事关国家民族复兴百年大计,心之所蓄,终不敢默。非敢故标高论,轻求更张。尚望公私贤达,详赐考虑。倘得于大中两级,妙选人才,各办试验学校一二所,侯成效确著,再谋推布,或亦稳健之一法也。
(三O,四,二O,《大公报》星期论文。)
附录【钱穆】《改革大学制度议》
今日大学教育有一至要之任务,厥为政术与学术之联系。抗战期间,后方政治之重要,不亚于前线之军事,其理尽人所知。而抗战结束以后,百孔千疮,万端待理,政治事业之重要与其艰巨,更将十百倍于今日。而政治事业之推动与支持,则首赖于人才。人才之培养,系唯大学教育之责。抑政治事业,就广义言之,不仅于居官从政。社会各方面各部门种种事业之推动支持,均有赖于适当之人才。亦必俟社会各方面各部门事业均有适当人才为之推动支持,而后其政治乃有基础可以发皇。在朝在野,相得益彰。此项社会各色中坚领袖人才之培养,亦唯大学教育之责。而不幸吾国最近二十年间大学教育之精神,似未注意于此。
吾国最近二十年间大学教育所注意之点,举要言之,约有三端。一曰校舍之建设,二曰图书仪器以及卫生体育种种物质上之设备,三曰院系之展扩,教师之罗致,以及课程之增新。
首言建筑。举其著者,北自北平清华,南至广州中大,东自首都中央大学,中越武汉,西至成都川大,其轮焉奂焉,门墙之美富,宫室之壮丽,彰彰在人耳目,此不得不认为是吾国最近大学教育精神贯注之一端。然与艰难兴邦,艰苦卓绝,实事求是之旨,则不能相符。居移气,养移体,而今日国家社会所需之人才,则在彼不在此。
次言设备。其一部分图书仪器之购置,与第三项相关,又一部分则属于生活起居上之讲究,与第一项相关。若大学校舍之建筑,稍能因陋就简,不事铺张,则内部设备,亦自大可省削也。
第三项当为大学教育最高目的所在。然仅仅注重于智识之传授,无当于人格之锻炼,品性之陶冶,识者讥之,谓此乃一种智识之稗贩。大学譬如百货商店,讲堂则其叫卖炫鬻之所也。抑就鄙见论之,即谓大学教育最高任务唯在智识之传授,而今日国内大学之院系析置,课程编配,亦大有可资商榷者。夫学术本无界划,智识贵能会通。今使二十左右之青年,初入大学,茫无准则,先从事各人之选科。若者习文学,若者习历史,若者习哲学,若者习政治、经济、教育。各筑垣墙,自为疆境。学者不察,以谓治文学者可以不修历史,治历史者可以不知哲学,治哲学者可以不问政治。如此以往,在彼目以为专门之绝业,而在世则实增一不通之愚人。而国家社会各色各门中坚领袖人物,则仍当于曾受大学教育之学者中求之。生心害事,以各不相通之人物,而相互从事于国家社会共通之事业,几乎而不见其日趋于矛盾冲突,分崩离析,而永无相与以有成之日。
再进而一究各院系课程之编配,则其细已甚。更有甚者,国难以前,国内最负时誉之大学,莫不竞务于院系之析置,教授之罗聘,以及课程之繁列。一学系教授往往至七八人,课目往往至一二十门。而此等课目,则皆此等教授之专门绝业也。二十左右之青年,初入大学,茫无准则,于选科之外,又继之以选课。治文学者,或治甲骨钟鼎,或治音韵小学,或治传奇戏剧,或治文艺创作,亦复各筑垣墙,自为疆境。其于文学之大体,则茫然也。其他治历史哲学以往者,亦复尔尔。近人有讥中国教育为一种循环教育者,其意谓受教育者无当于国家社会之用,仅能循环不息,仍以其受教者教人。此亦浅言之耳。今日一大学国文系毕业之学生,即深感不能担负中学国文教员之重任。何者,彼之所治,乃专门绝业,如甲骨、钟鼎、音韵、小学、传奇、戏曲、文艺创作之类,皆非中学国文课所需。中学国文课所需者,乃一略通本国文字文学大义之人才,而今日大学教育,即绝不注意乃此。今日大学课程之趋势,愈分愈细,如俗所云钻进牛角尖,虽欲循环,而不可得也。
概括言之,今日国家社会所需者,通人尤重于专家。而今日大学教育之智识传授,则只望人为专家,而不望人为通人。夫通方之与专门,为智识之两途,本难轩轾。吾国今日大学制度之渊源,袭自欧美。读吾文者,必将以欧美大学制度为护符而生抗议。然欧美政治社会与中国未能尽同。必俟社会政治各色各部皆有中坚领导人才推动支持,撑得一局面,粗粗安定,粗粗像样,而后专家绝业乃得凭借而发抒。欧美社会政治各方面比较已有一粗粗安定像样之局面,而中国则否。故中国大学教育所当着意植培之人才,自当与欧美稍异其趣。且就学术而论学术,一门学术之发皇滋长,固贵有专家,而尤贵有大师。大师者,仍是通方之学,超乎各部专门之上而会通其全部之大义者是也。一部门学术之有大师,如网之在纲,裘之有领,一提挈而全体举。今欧美著名大学之讲座,此等大师,往往有之。而中国挽近学术,一切稗贩自欧美,传其专业较易,了其通识则难。故今日国内负时誉之大学,其拥皋比而登上座者,乃不幸通识少而专业多。如此则将使学者不见天地之大,古今之全体,而道术将为天下裂。昔者庄生之所怖,行且再见于今日。况欧美分系分科之制度,亦已渐为彼中有识者所不满,而国内最近大学课程之变本加厉,则尚有非欧美之所能企及者乎?物极必反,穷则思变。其细已甚,不可为继。此今日大学课程之谓矣。
论者率谓大学教育,不当偏重智识之传授,即同时应注意及于学者人格之锻炼,品性之陶冶,于是而有导师制度之倡议。然就鄙见所及,则今日教育部所欲积极推行之导师制,乃与现行大学教育根本精神扞格不相融。若仅求于现行大学制度中硬插进一导师制度,正如于现行全部大学课程中硬插进一门党义与一门军事训练耳。上下相蒙,视为具文,固无不可。真欲求其收相当之效果,则非徒绝不可得,抑且必得其正相反者。
私意以为现行大学制度,实有根本改革之必要。而改革大纲不外两端。一曰缩小规模,二曰扩大课程。请先言缩小规模。窃谓将来之新大学,应以单独学院为原则。其主干曰文哲学院,理工学院,其他如农学院,矿学院,森林、畜牧、纺织、渔业等诸学院,不妨各就需要,择地设立(其年限不妨较文哲理工学院稍短)。唯法律学院与医学院,应以毕业文哲理工学院或肄业二年以上者入之,与他学院不平行。每一学院之学生数,以二百人至四百人为限,最多不得超过五百人。次言扩大课程。窃谓每一学院之课程,应以共同必修为原则,而以选课分修副之,更不必再为学系之分别。以文哲学院言,其课目应包括现有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教育等各系之主要课目,而设立略通大义之学程。如中外名著研读,中国文学史,中西通史,及文化大纲,中外人文地理,中西圣哲思想纲要,政治学经济学大纲,教育哲学及教育方法等。并应兼习科学常识,如天文、地质、生物、心理学等各门之与文哲学科相关较切者。此项共通必修之学程,应占大学全学程二分之一以上。学者于研习此项共通必修学程之外,同时亦得各就性近,分习选科。此项选科之开设,一方就各学院所聘教授学业之专长,一方亦兼顾各学科之重要部分,为学者开示途辙。各学科之课程不必求备,各学者之选习,亦不必求专。要之大学教育之所造就,当先求其为通人而后始乃及于专家。而细碎无当大体之学程,则尤以少设为是。关于理工方面,笔者一无所知,不敢妄有所述。唯尝询之于理工方面之通人及有志青年,亦多病今日学校开设学科之细碎,与夫基本智识之不够。则其受病,盖亦与文哲方面略似。窃谓亦当如文哲学院办法,理工合院,不更分系,多授基本通识,而于本国通史及中西圣哲思想纲要二科,亦必兼治,以药偏枯之病。然必有为今日造就专家教育辩护者,其论点计必举实用主义为依旧。唯即就实用言,通人达才之在今日,其为用尤其于专家绝业。十数年来,学者争以文科为无用,而竭力提倡理科。彼不知一国社会教育政治经济各方面苟无办法,则其自然科学亦绝难栽根立脚,有蒸蒸日上之望。今自抗战以来,学风之变,激而愈远。投考理学院之学生,群然转向而考工学院。试问理学院无基础,工学院前途何在。若就文法学院论,则哲学系早有关门之势,最近文学系亦渐渐有追随哲学系而闭歇之倾向。稍次为历史系,较盛者为政治系,尤盛者为经济系。试问一国之政治不上轨道,经济岂能独荣。亦未有其国人全昧于已往之历史,而政治可以有办法者。亦未有其人绝不通文学哲学,而可以通史学者。仅以实用主义谈教育,必使学者专务于谋出路,寻职业,自私自利,只图温饱。而整个教育精神,亦必陷于急功近利,舍本而逐末。尝发狂论,谓学者竞舍理学院入工学院,更不如离弃大学而入汽车行之为愈。教育精神自有其大者远者,此则唯通才达识者知之,擅一才一艺以绝业名专门者,往往不知也。
若就鄙见所及,创立不分系之学院制,其学成而去者,虽不能以专门名家,然其胸襟必较宽阔,其识趣必较渊博。其治学之精神,必较活泼而真挚。文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之智识,交灌互输,以专门名家之眼光视之,虽若滥杂而不精,博学而无可成名,然正可由是而使学者进窥学问之本原,人事之繁赜,真理之奥衍,足以激动其真情,启发其明智。较之仅向一角一边,汲汲然谋学成业就,有以自表见者,试问由其精神影响其事业,其为用于国家社会者孰大。必学术丕变,而后人才蔚起。上述国家社会各色各门之中坚领袖人才,可以推动支持一种事业,撑成一种局面者,殆将于此求之也。其有刻意潜精,愿毕生靖献于一种专门学术之研究者,则于普通学院之上复设研究院,以资深造。
若论人格之锻炼,品性之陶冶,此亦学业进行中应有之一项目。苟治学为人,可以绝然分为两事,则其学之与其人,亦居可见。依鄙论,大学有教授,即不必再有导师。若大学教育能有造就通才之师资,则其人格之锻炼与夫品性之陶冶,亦已一以贯之矣。更不必骑驴而觅驴,叠床而架屋也。诚使将来之大学,变为不分系别之独立学院,其校长与教务长对于全校四五百学生之生活与性情,必能熟悉无遗,因材施教,始有可能。而全校教授,最多亦不至超出二三十人之数,可由校长教务长斟酌尽善而加聘请。其学术行谊,精神意气之相投,较之今日一大学文法理工学院教授百许人相集合,牟牟然各不相认识,各不相闻问者,亦必判然有间。学者耳濡目染,较有轨辙可寻。教授之于学生,纵不能一一全识,亦必认得其十分之六七。(以不分系故)而学生之于教师,则大抵皆可全识,不致路途相遇,掉臂而过之。(以不分院故)所谓如家人父子然,以人格相感化者,不必在上者之提倡,而自有其境界。不然,如今日者,全校三四院,每院六七系。教授一二百,学生数千人。为校长者,能以权诈术数维持学校不闹风潮不罢课,已为幸事。学生如入五都之市,目迷五色,耳乱七音。教授之来也,如一沤之漂浪于大海,虽有深愿,莫知所施。非专门绝业,不足以撑门面;非标新立异,不足以耸观听。学风之弊坏既极,更何论于人格之锻炼,与品性之陶冶。
近人亦有目睹大学教育之弊病,而不能洞察其症结所在,遂提倡恢复宋明书院旧统者。然书院亦已陈之刍狗,非如海上灵方,百病皆效也。窃谓昔日书院旧制,虽有其特点,而近代大学制度,至少有胜于书院制者两端。一为讲堂授课制。原原本本,首尾条贯,表里精粗,无所不到。昔人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窃谓今之讲堂制,苟遇良师,则一年授课,实胜如十年之勤读也。二曰课目分授制。各就专长,分门别类,兼收广畜,不名一师,实足以恢张智能,开拓心胸。较之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言者,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计。书院制所特胜于现行大学者,在其规模之狭小,师生有亲切之味,群居无叫嚣之习。若如鄙论,将来新大学以单设独立学院为原则,则庶兼二者之长,而无二者之缺尔。
今国难方殷,大学教育之缺陷,方更彰著。昔日各大学之建筑设备,大多化为瓦砾,荡为灰烬。学校于播迁流离之余,亦莫不因陋就简。学课之其细已甚者,渐不足以餍学者之望。较者亦苦于穷搜擗摘之无所施其技,而几于倚席不讲。因势利导,庶其在是。窃谓来日之大学,贵乎艰苦卓绝,而不贵乎铺张扬厉。贵乎实事求是,而不贵乎粉饰门面。贵乎淡泊宁定,而不贵乎热闹活动。规模不厌其小,而课程务求其大。所以作人才而培邦本者,其影响于建国前途实非细鲜。粗发鄙愚,窃愿邦人君子一商讨之。
附录【钱穆】《从整个国家教育之革新来谈中等教育》
中国创办新教育,自前清同治初元迄今八十年,始终不脱两大病。一曰实利主义,一曰模仿主义。实利主义之病,在乎眼光短浅,不从本源处下手。模仿主义之病,则在依样葫芦,不能对症发药。其实二病仍一病也。病在始终缺一全盘计划与根本精神。我所谓全盘计划与根本精神之教育,当名之曰国家教育。而前清以来八十年之教育,则殊与国家教育无涉。当其最先所设学校,只限于广方言馆水陆师学堂乃至格致书院之类,充其量,不过欲造就少许翻译人才军事人才与制造机械之人才而止。学外国语言文字,根本只为外交作翻译之用。学格致,根本只为军事上种种机械制造之用。自始便无一段精神认识到国家教育之深处。此由一种短浅的实利主义作祟,而模仿主义亦自依随而起。此一病直到民国初年,科举既废,政体既改,国人渐渐觉悟教育不仅为翻译与制造。一时目光,渐渐从军事与外交转移到政治法律经济诸部门,又更进而推及于文哲历史艺术各类。当时乃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而溯源寻根,仍还自前清同光以来之思想一气呵成。所异者,前一期乃实利主义为主而模仿主义副之,此一期则模仿主义为主而实利主义副之。而紧接新文化运动之后者,乃为科学救国与科学教育之呼声。其所谓科学教育者,依然缺乏一根本精神,无当于国家教育之深旨。就其实,仍以实利主义与模仿主义为支撑。不过又复以实利主义为主而模仿主义为副,实利与模仿二者之间,稍有畸轻畸重之转变而已。此乃民十八以来之大体情形。风尚所趋,近几年来各大学新生投考,报工学院者异常拥挤,而理学院则寥寥。文法学院独一经济学系最盛,而经济系的课程,亦只偏向于银行簿计会计管理之类,绝少对经济学原理有兴趣者。哲学系最不受人注意。而五人中至少四人学西洋哲学,至多一人学中国哲学。文学方面则十人中至少八人学西洋文学,至多两人学中国文学。此乃当面之事实,事实后面透露出一种心理。此种心理之倾向,便足表示一时代之风尚。而此辈中学青年投考大学时之心理倾向及其风尚之来源,则不得不说是教育精神所感召。此种教育精神,直从前清同光以来,一路从源头上看,又从当前实际情形看,不能不说其仍只为实利主义与模仿主义之作祟。若非为实利主义,何以群趋工科而不习理科?若非为模仿主义,何以群习西洋文学哲学而鄙弃本国文哲?所以民国三十年来之新教育,似乎依然摆脱不掉模仿与实利。实利是其目的,模仿是其手段。实利非不该讲,模仿非不该有。然若仅以模仿希冀实利之心理与见解为国家教育之重心,则实利既不可得,而模仿亦且不可能。我们的教育精神与教育理论,实有再反省与再讨论之必要。
今当针对时弊,提出两口号。一曰文化教育,一曰人才教育。此两口号亦互为表里,乃主以国家民族传统文化来陶冶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文化教育可以纠正新文化运动以来之一味模仿。人才教育可以包括时下科学教育专重实利主义之偏狭。所谓人才教育者,不仅限于自然科学之一面,而政法经济文哲历史艺术诸门亦已兼容并包。此种人才,求其能真切爱护国家民族,求其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则必以国家民族自本自根之传统文化为陶冶。否则若其人对英国文学哲学英国历史艺术乃至英国一切政法经济之本末源委知之甚悉,而对吾本国之此诸项目一无所知,则其人中心爱护英国之真诚必较其爱护本国者为更深更切。而其人之服务于本国社会,势必多所扞格,多所膈膜,不能为本国国家民族所理想要求之人才。此理至为显明。科学可以无国界,政法经济文哲史艺诸科不能无国界。科学人才虽可由留学教育而造就,政法经济文哲史艺诸科之人才,则必自本自根由自己传统文化为陶冶,非外国教育所能代劳。若国内政法经济乃至文哲史艺诸门皆无人才,皆无出路,则纵有外国教育所代劳而造就之科学人才,亦将感英雄无用武之地之苦痛。故科学教育仅当为人才教育之一部门,当于国家教育之全盘计划下有其地位与效用。而国家教育之全盘计划,则必于国家民族自本自根之传统文化有较深之认识与重视。故讲求国家教育之全盘计划与根本精神,实舍文化教育与人才教育莫能当。
中等教育为国家教育之一环,故中等教育亦当以文化教育与人才教育为主体。若根据此项意见,则当前之中等教育实有多需改正之处。目前中等教育第一大病,在仅以中等教育为升入大学教育之中段预备教育。而大学教育之终极目标,则为出洋留学。换言之,出洋留学,乃不翅为吾国家教育之最高阶层。故国内各大学各科教科书,几乎十之七八以采用西洋原本为原则。大学新生,以先通一种外国文为及格标准。而进入大学以后,则以径读西洋原本教科书及进而选修第二外国语为普通之常例。通常所谓第一外国语者,大体乃为英文。故中学教育之中心责任,乃不啻为投考大学之英文补习学校。学生在各科学程上所化之精力,几乎强半为修习英语之时间。然若此学生将来并无升入大学之机会,则其研习英语之工夫亦强半等于白费。欲矫此弊,首宜厘革大学课程。尤要者,莫如一切教科书均以用本国文字为原则。中国兴学八十年,自有国立大学亦逾四十年。前清光绪二十四年举办国立京师大学筹备章程有于上海设编译局,各学科除外国文外,均读编译课本一条。乃至今逾四十年,国立大学各学科仍无编译完备之课本,仍要借用外国原本教读。抑且一般见解,不以此为可羞,转以此为可夸。此实四十年来国家教育之失败,亦四十年来留学教育疲缓不济事之奇耻大辱也。不仅大学各学科教本必需用本国文字编译者为原则,即各学科基本参考用书,亦当由国立编译机关作大量有计划之翻译。庶使学者省其攻读外国语文之精力,以从事于学科本身之精研与深究。尤要者,国家必设法提高本国大学之地位,勿再以出洋留学为国家教育之最高阶层。苟使此两事办有成绩,则庶乎可以走上文化教育人才教育之趋向。否则全国青年,当其有志向学,即日夕孜孜于外国语言文字之攻读。及其成学有立之最高阶段,又全付其责任于外国人之手。如是而言文化教育人才教育,真所谓南辕北辙,将愈趋而愈远。更不如缘木求鱼之仅止于不可得而已也。
国家教育若诚有意于文化教育与人才教育之两目标,则又有一事必当注意者,即国立大学当以文理学院为首脑,为中心。其他特殊专门学科如医工农矿渔牧诸类,不妨因地制宜,多设独立学院,与大学中心理工学院分道扬镳。盖前者为文化人才教育而设,后者则为养成职业技术之专门人才而设。两者旨趣不同,分之则两美,混之则两损也。若大学有此分设之规定,则中学问题亦迎刃而解。中学亦应分普通中学与职业中学两类。普通中学为文化人才之教育而设,职业中学则为养成职业技术之专门人才而设,性质亦复不同。凡受普通中学之教育者,主旨与大学中心文理学院之教育同,皆以国家民族传统文化陶冶真切爱护国家民族与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为主。是为国家教育之骨干。而各项中学职业学校与各项专门独立学院则如枝叶之附丽。其设科施教,不妨偏于实用,不妨模仿外国之成规,然皆非所语于国家教育之主干。
若如上论,普通中等教育之主要任务,实当以文化教育为手段,以人才教育为目标。换辞言之,即注重于国家民族传统文化之陶冶。经此一番陶冶而出者,则当期其为国家民族所理想要求之人才也。本此旨趣,中学教育之中心课务,实当以本国语言文字之传习为主。夫科学知识可以分门别类,而人生所需要之知识,实不尽于科学知识。因此有许多知识虽为吾人所必需,而往往无门类之可分。因此学校教育若以科学教育为中心,必将遗漏好许为人生所必要之知识。若以文化教育为中心,则此病可免。而文化教育之最重要者,则首推文字教育。一国之文字,即此国家民族传统文化之记录之宝库也。若使青年能读一部《论语》,读一部《庄子》,读一部《史记》,读一部《陶渊明诗》,彼之所得,有助于其情感之陶冶,意志之锻炼,趣味之提高,胸襟之开广,以至传统文化之认识,与自己人格之养成,种种效益,与上一堂化学听一课矿物所得者殊不同。然不得谓其于教育意义上无裨补。抑且毋宁谓教育之甚深意义,实在此而不在彼。今日中国学校中对于本国文字之教育,我无以名之,名之曰迁就之教育。夫教育宗旨本在悬一高深之标格,使低浅者有所向往而赴。迁就教育则不然。教育者自身无标格,乃迁就被教者之兴趣与程度以为施教之标格。夫学问有阶级,不可躐等,此义尽人皆知。然文字教育则有时贵乎投入亲验,使之当面觌体,沉潜玩索之久,而恍然有悟,豁然有解。此所谓欣赏,而阶级之制限有时为不适用。今国人每议本国文字为深玄难解,不知此当投入亲验。惟读《庄子》可解《庄子》,惟读《史记》可解《史记》,若先斥《庄子》《史记》为难读,先读其浅者易者,而文字文学之阶层亦重重无尽,若取迁就主义,则更有其尤浅尤易者。日亲浅易之读物,永不能达高深之了解。施教之标格日迁就,受教者之智慧日窒塞。此如希腊神话亚侠儿(Achilles)与乌龟赛跑,亚虽善走,将永远赶不上乌龟。何者,亚之脚步如必依照乌龟前行之距离为比例,而不许其痛快大踏步前进,则势惟裹足不前,而乃永无追出乌龟之望。今日中国中小学本国文字文学之课程,皆乌龟也。此种迁就主义,不知埋没冤屈了几许英才。今日中国一中学毕业生,彼乃无自己阅读本国古书之能力。彼乃不啻生在一无文化传统之国家。彼心神之所接触者,仅限于眼前数十年间之思想事物而止。彼之情感何从潜深?意志何从超拔?趣味何从丰博?胸襟何从豁朗?此等教育,大率为目前计,不为文化之传统计。此等教育所造就之人才,除却所谓科学知识外将一无所得。而今日中国中学大学中之教授外国文,则精神意趣,与前所云云者大异。彼尚不失有一标格,而强人以必赴。故即在中学生已有读莎士比亚之戏剧,雪莱之诗歌者。二十年来,各大学中学学生之晨夕孜孜披一卷而高声朗诵者,百分之百皆诵英文,绝无一人焉读本国文学者。若有之,其人必为侪偶所腹诽,所目笑,而彼亦将引为奇耻大辱。然此数十年来,试问国内造就几许真懂莎士比亚雪莱之文学者乎?以中国之大,有千人万人熟读莎士比亚雪莱不为多。独怪以中国之大,乃渐渐有寻不到能读本国文学本国古书之青年之情形。彼辈在中学校毕业,既未具备自己阅读本国文学本国古书之能力,彼之全部精力乃全费于研读外国书之准备。及其毕业以后,所入者乃中国社会,绝少继续研读外国书之机会,而中国文学中国古书虽日触于眼帘,彼固无此能力,亦无此信仰,并无此兴趣。彼乃不得不与学术界文化界相隔绝。即自大学毕业者,亦何独不然。彼辈大率能读外国书,而未必常有外国书可读。彼辈大率不能读中国文学古书,而彼辈终不能耐无书可读之苦。则一般阅读兴趣,乃不得不集中于时下新起之新文艺与宣传小册,以为消遣。故今日中国国内之学术空气,仅能存在于学校之内部,绝无法推广及于社会。而所谓学校内部之学术空气,又常汲源于外洋,非植根于本土。今日中国国家教育,乃尽力自掘传统文化之根,又尽力为移花接木之试验,而二三十年来之成效,则已大可见。若曰推行科学教育,则科学应重事物实验,不应白费学者心血于外国文字文学之研习。若曰推行文化教育,则中国自有传统文化。谓中国无有科学则可,谓中国无文哲史艺诸学则绝不可。谓中国政法经济诸学须参考外国新学则可,谓研究政法经济者可绝不理会中国已往自己传统则绝不可。若曰必全盘西化,则专通英文,决非全盘西化。若强中国人必兼通英法德俄各国文字,其事既难。若亦穷本竟源,先修希腊拉丁文,再从之自创一新式西化之中国文,一若彼中英法德俄诸邦之自十四世纪以下之各自创其新文字然,此又不可能之事也。然则中国学校何以必以研习英文为首务,我无以名之,名之曰模仿之教育。夫亦曰英国人读莎士比亚,我亦读莎士比亚而已。英国人读雪莱,我斯亦读雪莱而已。又知英国人尝舍弃希腊文拉丁文之研习而自创新英文,我斯亦舍弃我之古书古文而已。谓之模仿教育,谁曰不宜。夫曰模仿教育,犹逊辞也。刻实言之,则乃一种次殖民地之教育也。故今日中国国家教育之惟一出路,端在转移此种模仿教育之积习。若使中等学校之青年,于晨光曦微,晚灯煜烨之下,手一卷而高声朗诵者,非莎士比亚与雪莱,而为《论语》《庄子》《史记》陶渊明,则具体而微矣。
今日学校教育有一绝大困难问题曰训育,而中等学校尤甚。夫训教一贯,本非离教而别有所谓训也。今离教而求训,训必无效。教者非以已教,乃以己之所学教。己之所学在《论语》孔子,己之所教亦为《论语》孔子
所教非我之言,乃《论语》孔子之言。学者非欲其尊信我,乃欲其尊信《论语》孔子。由尊信《论语》孔子,乃亦尊信及于我。古语云,师严而道尊。然亦以道之尊而后师可严。又曰尊师而崇道。其实亦以道之崇而后师始尊。今学校以训育问题而牵连及于导师制度,深苦导师之不胜任而难其选。夫师之地位在其所教。若求导师,则中国往古圣哲豪杰,如孔子孟子老聃庄周以来,何啻数千百万,皆导师也。使学者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诵其文,若聆其言,不啻耳提而面命。潜移而默化,心领而神会,则既有教而训随之。今乃一切舍弃,曰此已死之陈人,已死之陈言,不足以为教,然则又孰足以为教?昔日小学校儿童所听古事如孔融让梨,如司马光剥胡桃,凡其所学,即可为训。今日小学校所学,大率乃一只狐狸三个小仙女之类耳。昔日中学生国文课颇读《史记·项羽本纪》之类,今日中学生则只读鲁迅之阿Q正传。昔日青年入学校,其背后尚有家庭父兄之教督。今日则全国家庭父兄皆已自承顽固,再不敢教督其子弟,转望子弟自学校携返新教训以焕发其家庭。故今日之青年,就文化传统言之,彼乃上无千古,下无百世,彼乃一无承续无蕲向之可怜虫也。徒日嬲其旁曰革新,曰创造,曰独立,曰自由。则无怪其日趋于犷獟而无文,桀黠而难教。故今日之教者惟有两途。一则曰为公民当云云,一则曰西洋人云云而已。夫公民仅限于奉公守法,仅限于政治之一角落,固未能渗透及于人生之全部。西洋人云云非不可教,然道听而途说,隔靴而搔痒,实不能深切著明也。今欲指导其成一理想的中国人。苟舍此二者,而为师者自以己意为教,曰我欲云云,则学生群起而哄之。然则将何以为教?曰必本于自己国家民族之传统文化以为教。教育即文化之一部分,今既剿截数千年传统文化,只许就目前当今以为教,是则教育脱离文化而成为无文化之教育,故其教育之收效也特难。青年在学校,已感其无可教,而谓一出学校,便可为国家民族理想需要之人才,此又必不可得之数也。
今再概括言之,则本于国家文化教育人才教育之旨趣,一普通中学生,必以能自己阅读本国已往古书古文为其毕业之起码标准。再本此标准而约略设计普通中学之课程,则关于各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之传授,其课程地位最多不当超过文字文学研习课程之一倍以上。而对于外国文字文学研习之课程与时间,最过亦不当超过对于本国文字文学研习时间之三分之一。犹不尽于此,一面尚当于大学校先培植能胜任愉快之中学国文教师,一面又当自小学校起再厉行改变国文国语迁就教育之通病,而后此新标准始有到达之希望。若论科学教育,则本不必多量注重于文字之研修。今既于普通中学外尽量多设各种独立学院,又国家设立大规模编译馆,尽量翻译外国各部门之重要书籍,而学者中之聪明特秀者,仍得于大学文理学院中精研外国文而为中外兼通之人才。此固于时下所主吸收西洋文学及提倡科学教育两无妨碍。必有此调整,而后中等教育乃有彻底更新之可能。否则就中学而言中学,缚手缚脚,左支右绌,殊无自由发展之余地也。
第7章 谁在保护消费者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社会上,除乞丐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全然靠别人的恩惠生活。”(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页)
我们的确不能靠恩惠而获得我们的饮食——但是,我们能全然靠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吗?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改革家和社会批评家们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利己心将使得卖方去欺骗他们的顾客。卖方会趁机利用顾客的单纯和无知,向他们漫天要价,并把劣等货塞给他们。卖方会哄骗顾客去购买他们不需要的商品。此外,批评家们已指出,假如你对市场听之任之,其结果还会影响到直接受害者以外的人们。它可以影响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饮用的水,我们所吃的食品的卫生。据说,为了保护消费者不受他们自己和贪婪的卖方的侵害,保护我们所有的人不受市场交易所产生的消极的毗邻效应的侵害,市场必须另行予以安排,使其臻于完善。
【译者按:消极的毗邻效应(spilloverneighborhoodeffects)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某甲的行动往往对某乙有不利影响,但又不承担任何责任。比如在同一条河流上,上游的化工厂以邻为壑,它所排出的污水对下游的酿酒厂和水厂会造成危害。】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指出的,对看不见的手的批评是有根据的。问题是,为了克服上述弊病而被推荐或采取的目的在于完善市场的那些安排,是不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精心设计的,或者是不是象我们所常见的那样,对策不会比弊病带来更大的危害。
这个问题在今天特别迫切。十几年前由一系列事件——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维尔对制药工业的调查,以及拉尔夫·纳德对通用汽车公司科维牌汽车“以任何一种速度行驶都不安全”的抨击——所展开的运动,使政府在市场上以保护消费者名义进行的干预,在广度上和性质上都起了较大的变化。
从1824年建立的陆军工兵部队到1887年建立的州际商务委员会,再到1966年建立的联邦铁路管理局,这些机构都是联邦政府为管理或监督经济活动而建立的,它们在范围、重要性和目的方面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几乎所有机构都管理某一行业,对该行业拥有明确规定的权限。至少从州际商务委员会建立以来,保护消费者——主要是其经济利益——已是改革家们公开宣称的目标之一了。
在新政以后,干预的步伐大大加快了——1966年共有三十二个联邦政府机构,其中一半是在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建立起来的。然而干预仍然是颇有节制的,并继续采用分别对各个行业进行干预的模式。1936年设立了《联邦登记册》,记载全部规章制度、申诉和涉及各种管制机构的其他事务,它起初颇为缓慢地,随后就急剧得多地扩大篇幅了。1936年它充其量只有三卷共二千五百九十九页,并在书架上占有空间六英寸;1956年增至十二卷,共一万零五百二十八页,占用书架空间二十六英寸;1966年达到十三卷,共一万六千八百五十页,占用书架空间三十六英寸。
接着,在政府的管制活动方面,出现了真正的迅猛扩展。随后十年里,建立的新机构不少于二十一个。这些新机构不涉及特定的产业,而是包括广阔领域:环境、能源的生产和分配、产品安全、职业保险,等等。除了关心消费者的经济利益,保护他们不受卖方的剥削以外,最近建立的各机构主要关心象消费者安全及其福利一类的事情,保护消费者不仅不受卖方、而且也不受他们自己的侵害。
政府用于所有新老机构的支出迅猛上升——从1970年不足十亿美元,剧升到1979年粗略估计的五十亿美元。物价一般说来大体上翻了一番,但政府上述支出则翻成五倍以上。被雇用于管制活动中的政府官员人数增加了两倍,从1970年的二万八千人增至1979年八万一千人,《联邦登记册》的页数则从1970年的一万七千六百六十页增加到1978年的三万六千四百八十七页,占用书架空间一百二十七英寸,即足足有十英尺的书架。
在这十年中,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变慢了。从1949年到1969年,私人企业全体雇员每一人时的产量——劳动生产率的一个简明而综合的指标——每年增长3%强;其后的十年中,每年增长还不到1.5%;在这十年的末期,生产率事实上是下降了。
为什么把这两种发展联系起来呢?一种发展是与保证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健康,保护洁净的空气和水有关;另一种发展则与我们怎样有效地组织自己的经济有关。为什么这两种好事情会发生矛盾?
答案就是,过去二十年里,无论标榜的目的如何,所有的运动——消费者运动、生态学运动、回到田园的运动、嬉皮士运动、有机食物运动、保护自然环境面貌运动、人口的零增长运动、“小的就是美妙的”运动、反核能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反增长的。它们反对新的发展,反对工业革新,反对加强利用自然资源。为此而建立的一批机构,把沉重的负担强加给一个又一个产业,以满足日益详尽和广泛的政府要求。这类机构阻止了某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并按政府官员规定的方式,要求工业必须把部分资金用于非生产性投资。
到目前为止,其后果是深远的,而且似乎今后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后果。正如大核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有一次说过的:“我们用了十八个月制造第一台核动力发电机;现在要十二年;这就是进步。”对纳税人说来,管制的直接费用,是其总费用中最小的一部分,政府每年用掉的五十亿美元,只是执行各种规章制度给各行各业和消费者带来的开支的很小一部分。按保守的估计,这笔费用一年大致为一千亿美元。这还没有把消费者因买到的商品很少有挑选余地和因价格高昂而遭受的损失计算在内。
政府作用方面的这种大变革,多半是随着公众主张所取得的成就而引起,而能和这种主张匹敌的则是很少的。若想一想什么产品目前令人最不满意并许久以来改进极少,那么,邮政业务、中小学教育、铁路客运业务无疑地会名列前茅。若想一想哪些产品或事业最令人满意并改进最大,那么家用器械、电视机和收音机、高保真度设备、计算机,而且,我们还可以加上超级市场和市郊商店区,将一定会列在那类名单的前列。
劣等货全都是政府的工业或政府管制的工业生产的。优质产品则全为私人企业生产的,这类企业同政府只有少许牵连,或者毫无关涉。然而,公众——或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已被说服相信,私人企业生产劣等货,我们需要有经常保持警惕的政府雇员监督商业机构,不让它们把包装漂亮但是不安全的商品,以过高的价格来欺骗那些不了解内情因而轻易上当的顾客。这种宣传运动进行得如此顺利,以致我们正把极为迫切的生产与分配能源的任务转移到我们提供邮政服务的人的手中。
拉尔夫·纳德对科维牌汽车的抨击,是破坏私人工业品信誉的运动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插曲,它作为一个例子,不仅表明了上述运动的威力,而且也表明了这一运动给人造成了多么错误的印家。纳德抨击科维牌车以任何一种速度行驶都不安全,结果引起公众对一系列商品的质量提出了疑问,政府建立了许多机构来管理商品。大约十年以后,上述机构之一终于对科维牌汽车进行了检验。他们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对比检验了科维牌汽车和其他汽车,并且得出结论:“同检验的其他各种汽车相比,1960—63型科维牌汽车是值得赞许的。”现在科维牌汽车迷俱乐部遍布全国,科维牌汽车已经变成收藏家的对象了。可是对于多数人,甚至见多识广的人说来,科维牌汽车仍然是“以任何一种速度行驶都是不安全的”。
铁路业和汽车工业是个极好的例子,说明受政府管制而免受竞争危害的产业与竞争非常激烈的私人工业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这两个产业部门服务于同一市场,并且基本上提供同样的服务即运输。前一个产业是倒退的,没有效率,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改革,只是内燃机替换蒸汽机。现今由内燃机牵引的货车,比起较早年代由蒸汽机牵引的那种货车,几乎没有区别。客车同五十年以前相比,而今开得更慢,服务更差劲。各铁路公司都在亏损,正在逐渐被政府接管。另一方面,汽车工业在国内外竞争和革新自由的刺激下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推广了一项又一项改革,以致五十年以前的汽车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消费者享受到利益——汽车工业的工人们和股东们也是如此。这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可悲的是汽车工业现在急剧地转变成政府管制的工业。在汽车工业中,我们眼前又出现了象过去那种阻碍铁路进步的状况。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受其自身规律的支配,这些规律不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条例,而是科学的规律。这种干预服从于强制力量,并按照与其创议者或支持者的意图或愿望很少相关的方向进行。我们已经考察了福利活动中出现的这种情况。当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时,不管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管制物价和劣等货的出售,还是为了增进消费者的安全,或者为了保护环境,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每一项干预法令都确立起权力地位。这一权力将怎样运用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运用,与其说取决于最初的创议者的目的与目标,倒不如说取决于那些得以控制上述权力的人们,取决于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州际商务委员会成立于1887年,是通过一场政治运动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机构,这场运动是由自称的消费者的代表——当时的拉尔夫·纳德之流——领导的。该委员会已经历了几代人,已有人对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与分析。它是一个很好的事例,说明了政府干预市场的发展史。
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丛林》揭露了芝加哥各屠宰场和肉店不卫生的状况,作为对随之而来的抗议的回答,最初于1906年建立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也已经历了几代人的时光。除了在规定的范围内起作用外,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还在较早的特定行业的管制型式与较近期的职能或跨行业的管制型式之间起着某种桥梁作用。它之所以能起这种作用,是因为1962年凯弗维尔提出的修正案使它的活动发生了变化。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全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环境保护局,都是管制机构的更现代化型式的范例——跨越行业进行干预,不太关心消费者的经济利益。对上述各机构进行全面的分析远远超出我们的讨论范围,我们只扼要讨论它们如何表现出同州际商务委员会和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所具有的共同趋势,以及它们为将来提出的各种问题。
虽然州和联邦政府对能源的干预是长期的立场,但在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禁运以及随后将原油价格提高三倍以后,这种干预有了量的飞跃。
正如我们将要说明的,假如我们不能依靠政府干预来保护我们这些消费者,我们能够依靠什么,市场采取什么方法来达到这种目的,以及这些方法如何能得到完善?
州际商务委员会
南北战争以后,接着是史无前例的铁路扩张——以1869年5月10日在犹他州普罗孟塔利钉进用黄金铸成的最后一颗道钉为象征,标志着联合太平洋铁路和中央太平洋铁路的接轨和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的完工。不久建成了第二条、第三条、甚至第四条横贯大陆的铁路。1865年已经营业的铁路有三万五千英里;十年以后,接近七万五千英里;到1885年超过了十二万五千英里。1890年已有一千条独立营运的铁路。铁路遍布全国各地,通向每一个偏僻的村庄,横贯整个大陆。美国的铁路线长度超过了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铁路线长度的总和。
竞争在当时是激烈的。其结果,货运和客运运费往往很低,恐怕是全世界最低的。自然,铁路公司人员曾抱怨过“无情的竞争”。每当经济动荡,在经济周期性衰退的一击之下,一些铁路公司便陷入破产并转归其他人,或者干脆关门大吉。经济复苏时,铁路建筑的另一高潮便随之而到来。
当时的铁路公司人员彼此联合,组成联营集团,并按照利润水平确定运费和瓜分市场,试图以此改善他们的处境。令他们沮丧的是,各种协定经常遭到破坏。只要一个联营集团的其他成员不降低运费,任何一个成员就能通过削减运费和从其他成员那里抢走生意而获利。当然,他不能公开削减运费,只能隐蔽行事,要使联营集团的其他成员尽可能长久地蒙在鼓里。于是受优待的托运人得到秘密的回扣,各公司对不同地区或不同商品订有差别费率。运费的削减迟早会为人知道,联营集团也就随之而垮台。
在象纽约与芝加哥这样距离遥远、人口稠密的地区之间的竞争,当时是非常激烈的。托运人与旅客们可以在由不同铁路公司和沟通两地的运河水运公司营运的一些交错的线路中进行选择。另一方面,这些铁路的任何一条较短路段中,例如在哈里斯堡与匹兹堡之间,也许只有一条铁路。那条铁路拥有某种垄断地位,只是容易受到可替代的运输方式的竞争,诸如运河或河流等运输方式。当然,这类铁路总要尽可能利用其垄断地位,收取尽可能高的运费。
一种结果就是,由各短程运输——或者甚至一段短程运输——收取的运费总额,有时大于从两个远距离地点之间的长程运输所收取的全部运费。诚然,没有消费者抱怨长程运输的运费低廉,但是,他们确实抱怨短程运输的运费高昂。同样,在秘密的运费削减战中获得了回扣的、受到了优待的托运人不会有怨言,而那些没有得到回扣的托运人,则对“差别定价”怨声载道。
铁路公司是当时的主要企业。它们的地位非常显眼,相互竞争激烈,同华尔街和东部财团有密切联系,报纸上报道的金融控制和欺诈事件很多都与它们有关。各铁路公司成了天生的靶子,特别是中西部农民们攻击的靶子。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发生的格兰其运动,对“垄断的各铁路公司”进行了攻击。农民们通过绿背纸币党、农民同盟等组织联合起来了。所有这些组织都在议会大厦进行鼓动,要求政府管制货运的费用及活动,并往往取得成功。平民党不仅要求对铁路公司施行管制,而已要求彻底的政府所有制和政府经营,威廉·哲宁斯·布利安是通过平民党而出名的。当时的漫画家们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他们把铁路公司描绘成章鱼,章鱼在扼杀国家,在对国家施加极大的政治影响(各铁路公司确实干过这些事情)。
【译者按:格兰其(grange)指1867年在美国开始成立的协进农民会,即全国性保护农民利益的田庄农民组织。绿背纸币党(GreenbackParty)系1875年成立的美国农业家的政党,它反对当时美国政府的收缩通货政策,争取维持廉价币值,以利于农民清偿南北战争中的负债。农民同盟(Farmers’Alliance)为1882年在美国北部成立的农民组织。平民党(PopulistParty)于1892年在美国成立,针对当时美国政府的通货收缩政策,它标榜自由铸造银币的纲领和一般的反对垄断的方针。】
当反对铁路公司的宣传运动高涨的时候,有些有远见的铁路公司人员认识到,他们能使这场运动转而对他们有利,可以利用联邦政府去执行他们确定价格和划分市场的协定,保护他们不受州和地方政府的侵犯。他们加入改革家的行列,一起支持政府管制,其结果是1887年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建立。
大约过了十年,州际商务委员会才得以充分发挥作用。到那个时候,改革家们已在进行另一场改革运动了。铁路只是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之一。他们已达到了目的,他们只偶尔粗略地查看一下州际商务委员会正在做的事情,而没有很大兴趣去领导铁路公司干更多的事情。对于铁路公司人员说来,情形就完全两样了。铁路就是他们的事业,是和他们有关的头等大事。他们准备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花费在铁路上面。而且,除了他们外,有谁能够充当州际商务委员会的职员并去管理这个机构呢?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利用该委员会去谋取他们自己的利益。
第一任政府专员是托马斯·库利,他多年来是代表各铁路公司利益的律师。他和他的同事们向国会要求更大的管制权力,并且被授予了这种权力。正如克利夫兰总统的司法部长理查德·J·奥尔尼,在州际商务委员会刚刚成立六年的时候给伯林顿和昆西铁路公司董事长、铁路巨头查尔斯·E·珀金斯的一封信中所说的:
在目前州际商务委员会的职能受到各法院限制的情况下,它是或者可以使之成为对铁路公司非常有用的机构。它平息了公众要求政府对各铁路公司进行监督管理的喧闹,而在同时这一管理几乎完全是名义上的。但是,这样的委员会历时愈久,就会愈多地倾向于采取商业和铁路公司对事物的看法。这样,该委员会将变成介于各铁路公司与人们之间的一种障碍,保护铁路的利益免受轻率而粗鲁的立法的侵犯。……明智的办法不是毁灭该委员会而是利用它。
州际商务委员会解决了长程运输或短程运输问题。该委员会做到了这点主要是通过提高长程运输的收费率,使之等于短程运费的总和,你得知这一情况是不会惊奇的。除了顾主以外,人人都高兴。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委员会的权力强大,它开始对铁路公司的各种业务实行日益严密的控制。此外,权力从各铁路公司直接选出的代表那里转移到了人数日多的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手中。可是,这对于各铁路公司没有什么威胁。许多官员都来自铁路行业,他们的日常业务是同铁路人员打交道,因而他们未来发迹的主要希望是同铁路公司联系在一起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货运汽车作为长途运输工具出现时,对铁路产生了真正威胁。州际商务委员会坚决维持了铁路公司异常高昂的货运费率,使汽车货运业得以飞速发展。后一行业是不受管制的,并具有高度的竞争性。拥有购买一部运货汽车资本的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该行业。在要求政府管理铁路公司的运动中,人们提出来的主要理由是:铁路公司是垄断企业,对它们必须加以控制,以阻止它们剥削公众,但这一理由对于汽车运货无论如何是不成立的。要找到比汽车货运业更能满足经济学家的所谓“完全”竞争条件的行业,那是困难的。
然而,上述情况并没有阻止各铁路公司去鼓动要把长途汽车货运置于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管辖之下。并且,铁路公司成功了。1935年的汽车运输法赋予州际商务委员会管理汽车运输业者的权力——以保护铁路公司,而不是保护消费者。
汽车货运重复了铁路的历史。它组成了卡特尔,收费率被固定下来了,线路被划分了。随着汽车货运业的发展,汽车货运业的代表对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取代了铁路公司代表的统治地位。正如保护铁路公司免受货运汽车的侵害一样,州际商务委员会已成为全力保护汽车货运业免受铁路公司以及不受管制的货运汽车侵害的机构。尽管如此,该委员会只不过是把保护其官员的利益掩盖起来罢了。
为了能在各州之间开展运输业务,一个汽车货运公司必须具有州际商务委员会签发的执照,即载明便利公众且属需要的执照。1935年国会通过汽车运输法后,州际商务委员会对一下子提出来的大约八万九千份申请执照的报告书,只批准了大约二万七千份。“从那时以来……该委员会一直非常不愿意批准新商号参加竞争。而且,开业的汽车货运商号的合并与破产,减少了这些商号的数目,从1939年的二万五千多家减为1971年的一万四千六百四十八家。在同一时期,受该委员会管辖的在各城市之间营运的货运汽车运载的吨位数增长了,从1938年的二千五百五十万吨增加到1972年的六亿九千八百一十万吨,增加了二十六倍。”
执照是可以买卖的。“运输量的增加、商号数目的减少以及运费管理局和州际商务委员会对运费竞争的干预。大大增加了执照的价值。”据托马斯·穆尔估计,1972年执照的价值总额介于二十至三十亿美元之间——只有这一数字可以衡量出政府确立的垄断地位的价值。对于拥有执照的人们来说,上述价值构成财富,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说来,却是一种由政府干预所带来的损失,而不是一种生产能力。每种研究都表明,取消州际商务委员会对汽车货运的管制,会使托运人的花费急剧地降低——穆尔估计或许会降低四分之三。
俄亥俄州的一家汽车货运公司,戴顿航空货运公司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它有一张州际商务委员会签发的执照,执照特许它从戴顿运货至底特律。为在其他线路上运货,这家公司不得不从州际商务委员会执照的持有者手里,包括一个连一部货车也没有的持有者手里购买运货权。为取得这种特权,它每年得付出十万美元。这家公司的老板曾试图买下某些线路的执照,但迄今为止没有成功。 该公司的一位名叫马尔科姆·理查兹的顾主说:“非常坦白地讲,我不知道为什么州际商务委员会止步不前,什么都不干。据我所知,这是第三次我们支持戴顿航空货运公司的申请,以便帮助我们省钱,帮助自由企业,帮助国家节约能源。……所有开支最后都要由消费者来付。”
戴顿航空公司的一位老板特德·哈克补充道:“就我个人而言,在州际贸易中没有自由企业。自由企业在我国已不复存在了。你不得不为此而付出代价,而且必须付出十分昂贵的代价。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必须付出代价,而且消费者也得付出代价。”
但是,另一位老板赫谢尔·温默却从另一方面来看问题,他说:“我不想同已经获得州际商务委员会执照的人进行争论,只是想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国,但从1936年州际商务委员开始行动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新成员加入汽车货运业。他们不准新成员进入该行业,不准他们同已营业的那些成员竞争。”
我们推测,这就是我们在铁路人员和汽车货运业务者中间一再遇到的反应:给我们执照或者让我们自行放弃各种规章,行;停止签发执照或者废除政府管制体制,不行。考虑到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上述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让我们再来看铁路问题,政府干预的最终影响目前仍未消失。日渐增多的各种严格的规章,使铁路公司不能作出有效的调整,来同小汽车、公共汽车和飞机争夺长途客运业务。铁路公司再一次求助于政府,这一次是以全美铁路客运系统的形式实行客运国有化。货物运输也实行了国有化。紧接着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触目惊心的破产之后,通过联合铁路公司(Conrail)的创立,东北部的许多铁路货运线路实际上国有化了。至于其他地方的铁路行业,前景也十分相似。
飞机运输重演了铁路运输和汽车运输的历史。1938年成立了民用航空委员会,当时由它管理的国内主要(即干线上的)航空公司为十九家。尽管空运量大大增加,尽管对“方便公众并满足公众需要的执照”的申请极多,但现在国内航空公司的数目却减少了。不过,飞机运输的历史同铁路运输和汽车运输的历史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并非最不重要的原因有:一家大国际航空公司的有胆量的英国老板弗雷德·莱克,成功地削减了横越大西洋航线的运费,以及民用航空委员会前任主席艾尔弗雷德·卡恩的个性与能力——近来在行政和立法两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废除了对飞机运输费的管制。对于某一领域来说,这在摆脱政府控制、争取较大自由方面,是人们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它取得的显著成就——航空公司的低运费和高收入——促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废除了对地面运输的管制。然而,一些强大的势力,特别是汽车运输业中的势力,正在组织反扑,所以到目前为止,废除管制仅有极微小的可能性。
最近,航空业中也出现了长短途运输问题,而且附带着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插曲。航空业中的运费差别正好同铁路行业中的差别相反,短途运费反而比长途运费低。事情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该州的面积很大,设立若干家大航空公司不成问题,它们的飞机可以只在该州境内的航线上飞行,结果它们可以不受民用航空委员会的管制。在旧金山与洛杉矶之间的航线上,各公司激烈竞争,产生了一种州内运费,它比民用航空委员会批准州际航空公司对同样航程收取的运费低得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1年自称为消费者保护人的拉尔夫·纳德,向民用航空委员会提出了关于上述差别的控告。而事有凑巧,在这之前,纳德的一家子公司公布了一份有关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出色分析报告,着重说明了长短途运输的区别对待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关于怎样解决航空公司的问题,纳德几乎不可能抱有任何幻想。正象研究政府管制的学者所预料的那样,民用航空委员会的裁决要求各州内航空公司提高它们的运费,以赶上民用航空委员会许可的运费水平,这一裁决后来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幸亏这一裁决由于法律上的各种细节问题而没有执行,并且可能因废除对航空运费的管制而无效。
州际商务委员会的例子说明了什么是可以称之为政府干预的合乎规律的历史。一种真实的或想象的灾难,要求人们采取某些行动。于是出现了政治联盟,由真诚而高尚的改革家和同样真诚的有关各方所组成。联盟成员的目标(例如对消费者的低价格和对生产者的高价格)虽然互相矛盾,但却被“公众利益“”公平竞争”等漂亮词藻掩盖了起来。该联盟说服国会(或一个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的序言充满了动听的词语,而法律正文则授予政府官员“干某件事”的权力。高尚的改革家们感受到了一种胜利的喜悦,并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新的事业上去。有关的各方则尽力确保上述权力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使用。他们一般都是成功的。成功本身产生了自己的问题,于是通过扩大干预范围来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官员分享利益后,甚至连当初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不再得到好处。最终的结果往往与改革家的目标完全相反,并且一般说来,达不到特殊利益集团的目标。然而,这项政府活动确立得非常牢固,同时,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又与它联系在一起,以致废除原有的立法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新的政府立法被用来对付由过去立法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一个新的循环由此而开始。
州际商务委员会清晰地展示了这些步骤的每一步——从对它的成立负有责任的不同寻常的联盟起,直到因全美铁路客运系统成立而引起的第二个循环的开始。该系统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它在许多情况下不受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管制,因而可以做州际商务委员会不准许单个的铁路公司做的事情。自然,冠冕堂皇地讲,建立全美铁路客运系统的目的是改善铁路旅客运输。这个系统得到了各铁路公司的支持,因为它将允许取消当时存在的许多客运业务。本世纪三十年代出色的和赚钱的客运业务每况愈下,由于飞机和私人汽车的竞争,它变得无利可图了。然而,州际商务委员会却不准许各铁路公司削减客运业务。全美铁路客运系统现在既允许削减客运业务,又对保留下来的那些客运业务予以资助。
假如根本没有建立州际商务委员会而是让市场力量起作用,那么,美国今天就会有一个令人满意得多的运输系统。在竞争的刺激下,铁路行业会取得更大的工艺改革,铁路公司会根据运输量的不断变化对线路进行更为迅速的调整,铁路行业也许会因此而小一些,但效率会更高。旅客运输可能为较少的公众服务,然而车辆和设备则会比现在精良得多,服务也会更为周到和迅速。
同样,由于效率的提高和浪费的减少,汽车货运公司的数目将增加,而运货汽车的数目可能减少。现今的浪费表现在回程放空车,以及州际商务委员会要求一些运输公司采取迂回公路线等方面。汽车运输费用将降低,而服务则更好。凡让领有州际商务委员会执照的公司运送过个人行李的读者,会毫不犹豫地同意上述判断。虽然我们不是商业托运人,但我们猜想他们也会同意上述判断的。
整个运输业的状况会与现在完全不同,也许会更多地采用联合运输方式。近年来,少数赚钱的私人铁路营业项目之一,是同一列火车既运送旅客又运送他们的小汽车。铁道平车运输方式无疑会远为迅速地被采用,而且会出现其他许多联合运输方式。
听任市场力量起作用,很难料想结果会是什么,但这正是让市场力量起作用的主要理由。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用户对某项运输业务的评价不高,不愿为它支付价格,或同意支付的价格不能使提供这项服务的人获得的收入高于他从事其他运输业务可能获得的收入,那么,这项业务就无法维持下去。用户和生产者都不能慷他人之慨,来维持一种满足不了上述条件的服务业务。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与州际商务委员会不同,联邦政府保护消费者的第二项主要措施——1906年通过的食品和药物法——不是起因于对高价的抗议,而是起因于对食品卫生的关心。当时是揭露丑闻的时代,是记者进行调查的时代。厄普顿·辛克莱被一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纸派到芝加哥,去调查牲畜围场的状况。他根据这次调查出版了著名小说《丛林》,他写这部小说本来要引起对工人的同情,但是小说却更多地激起了人们对肉类加工不卫生的愤慨。正象辛克莱当时所说的:“我瞄准的是公众的心,但却击中了公众的胃。”
早在《丛林》这部小说问世并激起公众要求制定有关法律的感情以前,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和全国禁酒协会等组织已经成立了全国食品与药物卫生代表大会(1898年),目的是开展宣传运动,促使国会颁布禁止出售假药的法令。当时出售的大部分假药都掺有大量酒精,因而酒精被当作药品来出售和消费。面对这种情况,禁酒组织怎么能不开展斗争呢。
在这里,特殊利益集团也加入了改革家的行列。肉类罐头厂的老板们“在这一工业的历史中早已意识到,使顾主中毒对他们是无利的,特别是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更是如此,在这样的市场上,消费者可以选择其他厂商的产品。”他们特别担心欧洲各国借口屠宰的牲畜有病,限制从美国进口肉类。他们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一机会,让政府证明他们出口的肉类是无病菌的,而且让政府支付检验费。
另一特殊利益集团是药商和医生,他们通过其职业联合会发表意见。同肉类罐头厂的老板相比,或者同州际商务委员会成立时的铁路公司相比,药商和医生的卷入较为复杂,单纯经济方面的考虑较少。他们的经济利益是明确的:如果专卖药和假药由江湖医生或其他人直接卖给消费者,那将同他们的业务相竞争。此外,药商和医生还从职业上关心现有的各种药品,敏锐地知道那些自称能医百病(从癌症到麻疯病无所不医),但实际上疗效甚少的药品给公众带来的威胁。热心公益的精神同自身利益相一致了。
1906年的法令主要限于检查食品和给专卖药加标签,不过由于偶然的原因而不是事先计划,它也管理处方,这一权力是很久以后才加以运用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前身隶属农业部。大约十五年前,不论是最早的机构还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制药工业都没有多大影响。
1937年年中磺胺问世以前,几乎没有制造出任何值得一提的新药。其后,一个化学家力图使磺胺对不能服用胶囊的病人发生疗效,结果就发生了所谓“特效磺胺”灾难。他所使用的溶剂和磺胺的化合物证明是致命的。悲剧的结局是“一百零八人死亡——其中一百零七名是服用了‘特效药’的病人,一名是畏罪自杀的化学家。”“从上述……经验中,药品制造商认识到了出售这类药物可能担负的责任,因而在投放市场前开始进行安全试验以避免类似事件的重演。”同时他们认识到政府的保护对他们可能是有利的。结果,1938年通过了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令,这一法令把政府管制扩及到广告与商标,并且要求所有的新药品在它们进入州际贸易之前,在安全方面须经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管理局应于一百八十天以内批准或驳回申请。
另一悲剧,即1961—1962年的撒利多迈德事件发生以前,制药工业及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之间具有亲如手足的共生关系。根据1938年法令的规定,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准撒利多迈德进入美国市场,只是医生为作实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用这种药物。当一些报告披露了欧洲的孕妇服用撒利多迈德后生下了畸形胎儿的消息时,就连医生也不能以实验为借口使用这种药物了。继之而来的抗议浪潮冲击了1962年的修正案,这些修正案是参议员凯弗维尔1961年对制药工业的调查引起的。上述悲剧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修正案的攻击矛头。凯弗维尔最初指控的是价格,即价值可疑的药品售价过高——这是关于垄断企业剥削消费者的一般性的抱怨。但国会通过的修正案则把矛头更多地指向质量问题,而不是价格问题。这些修正案“在1938年法令规定的安全检验之上,又加上了功效检验要求,同时取消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处理新药申请书方面所受的时间限制。一种新药只有得到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也就是说只有当它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药品符合1938年法令的安全要求,而且在其未来的使用中可以达到预期效果时,该药品才能在市场上出售。”
1962年的修正案是同下面列举的一系列事件相一致的,它们使政府的干预活动剧增,同时改变了政府干预的方向。这些事件是:撒利多迈德悲剧;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它发动了环境保护运动;以及有关拉尔夫·纳德的“以任何一种速度行驶都不安全”的辩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促进了政府作用的改变,而且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积极主动得多。对于环己基氨基磺酸盐(cyclamates)的禁止以及要禁止糖精的威吓。受到了多数公众的注意,但是,这些决非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最为重要的行动。
在1962年修正案中达到最高点的那些立法目标。没有人会不同意。当然,应该保护公众免受不安全而没有疗效的药品的侵害。然而,也应该促进新药的发展,应该把新药尽可能快地供应给那些能从新药中得到疗效的人。正象常有的情况那样,一项有益的目标同其他一些有益的目标发生了冲突。一方面的安全与谨慎,可能在另一方面意味着死亡。
【按:这个可以靠官方认证协调提供新药的人和试验新药的人的关系。】
重要的问题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管制在协调上述各个目标方面是否有效,是否有更好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已有人详细地研究过这两个问题。当前,已有大量证据表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管制是有损于生产的,它阻止生产和销售有用的药物带来的害处,大于它禁止出售有害的或无疗效的药物带来的好处。
政府管制对新药品的创新率产生了极大影响:1962年以来,每年推广的“新化学物质”的数目下降了50%以上。同样重要的是,对一种新药品说来,得到批准要花长得多的时间,而且,发明一种新药品的费用增加了许多倍。费用的增加是同政府批准时间的拖延有一定的关系。根据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的估计,当时发明一种新药品的费用约为五十万美元,从试制到投入市场约需二十五个月。如果计入自那时以来的通货膨胀率,现在发明一种新药花费一百万稍多一点美元也就够了。但1978年“要使一种新药进入市场,得花费五千四百万美元,需要大约八年的努力”——也就是说所需费用增加一百倍,所需时间增加三倍,而与此相比,一般物价则仅仅上涨了一倍。其结果是,各医药公司在美国已没有力量来为患有罕见疾病的病人发明新药品,它们越来越多地依赖销售量大的药品。长久以来在新药品发明方面居于首位的美国,现在迅速地落到了后面。而且,我们甚至不能从国外发明中得到充分的好处,因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往往不承认国外有关机构对药品性能的鉴定。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同铁路客运一样,对新药发明也实行国有化。
由此而产生的所谓“药品时滞”,表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在药品供应上存在的差异。例如,罗彻斯特大学药品发明研究中心的威廉·沃德尔博士提出的一份详尽研究报告表明,许多在美国买不到的药品在英国可以买到,而在英国买不到的药品在美国同样难于买到,而且在上述两个国家,可买到的药品投入市场所需要的时间,平均算起来在英国要快一些。沃德尔博士在1978年说:
某些很有疗效的药品在美国买不到,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如英国却可以买到,如果调查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许多美国病人正是因为缺乏这些药品在忍受病痛的折磨。例如,有一两种称为贝他——封阻剂(Betablockers)的药品,现在发现它们能防止心脏病患者因突然发病而死亡,也就是说能够防止冠状动脉因心肌梗塞而死亡。假如在美国有这类药品,它们一年中可以拯救上万条生命。在1962年修正案通过后的十年里,医治高血压——即为了控制血压——的药品在美国没有一种得到批准,而英国却批准了好几种。在全部心血管领域,从1967年到1972年的五年期间,仅一种药品得到了批准。这是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组织机构上存在的众所周知的问题相联系的。
与病人有关系的是,治疗方案过去常常由医生和病人来决定,而现在则越来越多地由联邦一级的专家委员会来决定,这些委员会及其上属机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一非常偏重于避免危险,以致使我们常常能够得到较为安全的药品,但却得不到有效的药品。最近我从上述一些咨询委员会那里听到一些值得重视的言论。它们在考虑某些药品的取舍时经常说,“患有如此严重的疾病的人不多,无需在市场上广泛出售这种药品。”如果你努力干的事情,是为了全体居民的利益而把药品的毒性减到最小程度,那是很好的;然而,如果你碰巧是那“人数不多的病人”之一,也就是说你患有一种极为严重的疾病或一种很罕见的疾病,那么你则交了恶运。
假定所有这一切都是事实,那么不让危险的药物进入市场,防止撒利多迈德这种药物引起一系列灾难,能否证明所付出的代价是合理的呢?萨姆·佩尔兹曼根据以往的事实对这个问题作了非常仔细的研究,而且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上述做法的害处大大超过了好处。他解释他的结论部分地是通过指出这一点:“1962年以前,市场使无效药品的卖主受到的惩罚似乎已经足够了,不需要管制机构再来插手干涉。”生产撒利多迈德的各厂家终究支付了几千万美元的赔偿费而收场。这对防止任何类似事件的发生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当然,错误——撒利多迈德悲剧就是一个错误——仍将发生,但将在政府的管制之下发生。
事实证明了一般推论的正确性。尽管愿望是良好的,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实际上阻挠了新的可能有用的药品的发明和销售。
如果你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一名官员,负责审批一种新药品,那就可能犯两种很不相同的错误:
1、批准一种新药品,它具有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即导致大批人的死亡或受到严重损害。
2、拒绝批准一种药物,而这种药物能拯救许多生命或减轻巨大的痛苦,并且没有不良的副作用。
假如你犯的是第一种错误,批准生产撒利多迈德,每家报纸就会在头版刊登你的名字,使你大为丢脸。假如你犯的是第二种错误,谁又会知道呢?知道此事的只有推销这种新药的药商和若干研制这种新药的药剂师和医生。前者会被斥为不顾人民死活的贪得无厌的商人,后者发发牢骚也就没事了。那些生命本来可以得到挽救的人们不可能提出抗议。他们的家人也无从得知心爱的亲人是由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一名素昧平生的官员的“谨慎小心”而丧失其生命的。
销售撒利多迈德的欧洲各医药公司受到了攻击,而不批准在美国使用撒利多迈德的那位妇女(弗朗西斯·O.凯尔西博士,曾由约翰·F.肯尼迪授予一枚政府优异服务金质奖章)则获得了声誉与名望。你究竟更急于避免哪一种错误,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怀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愿望,你或者我,假如处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官员的地位上,一定会趋向于拒绝或推迟批准许多好的药品,以便避免批准一种具有副作用的药品,引来一则值得报道的新闻,哪怕这种可能性很小。
这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因制药工业的反应而加强了。这种倾向导致过分严格的标准。得到政府批准要花更多的钱,要等待更长的时间,要冒更大的风险。研究新的药品带来的好处减少了。各公司不再那么害怕竞争者的研究工作取得新成果。现有各厂商和现有各种药品受到保护不要竞争的影响。新的参加者受到阻挠,研究工作可能集中在争论最小即革新最少的方面。
我们当中一人在1973年1月8日出版的《新闻周刊》上提出,因为上述种种理由,应该取消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后来该刊物收到了药厂工作人员的一些信件,信中谈到了他们自己的一些不幸经历,从而证实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阻碍药品的发明这一断言。但是,大部分人也发表了如下的看法:“和你的意见不同,我认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应该取消,但是我确实认为它的权力应该”这样或那样地加以改变。
其后,以“汪汪叫的猫”为题的一篇文章(1973年2月至9日)答复说:
有人说:“如果猫能汪汪叫,我希望有一只猫。”你对这种人会有什么看法?实际上他的这种说法同你下面的说法是完全一样的:如果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行为符合我的想法,那我将支持它。说明猫的特征的生物学法则,比起说明政府机构在其一旦建立后的活动的政治法则,并不更为严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活动的方式及其有害的后果,并非偶然的原因所造成,也不是人们容易改正的某种错误所造成,而恰好象喵喵的叫声同猫的本能有关系一样,是该管理局成立本身的结果。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你承认不能任意把特征归因于各种化学和生物的实体,不能要求猫发出汪汪的叫声,也不能要求水燃烧起来。那你为什么假定在社会科学中情形是不同的呢?
人们普遍错误地认为,各种社会机构的行为是可以任意改变的。这是多数所谓改革家犯的根本错误。这种错误说明为什么他们如此经常地感到,过失在于人而不在于“制度”;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赶走坏人”,让好人管事。这种错误说明他们的各项改革为什么在表面取得成功时,常会走上歧途。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带来的害处,并不是主管人的无能造成的,除非说人类本身就是无能的。他们大都是有才干的和忠实的公务人员。然而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对主管某一政府机构的人的行为的影响,要比他们对该机构活动的影响大得多。无疑会有例外,但例外是极少的——差不多象汪汪叫的猫那样稀少。
上述情况并不意味着有成效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但是,要使改革成功需要考虑支配政府机构活动的政治法则,而不要单纯责备政府官员效率低、浪费严重,或者怀疑他们的动机,觉得他们没有真正卖劲干活。凯弗维尔修正案改变了对公务人员的压力和刺激,在此之前,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虽然也带来害处,但要比现在少得多。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作为例子说明了管制活动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发生的变化。这个委员会跨越各个产业部门。它关心的主要不是价格或成本,而是安全。它拥有广泛的处理权限,并仅在最一般的授权条件下活动。
1973年5月14日正式成立的上述“委员会,被授予特别权力,保护公众不因消费品具有过大危险而遭受伤害,帮助消费者评价这些产品的安全,制定有关消费品安全的标准,在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把上述标准相互抵触的地方减少到最低限度,并调查研究消费品造成死亡、疾病和伤害的原因及其预防方法。”
该委员会的权限适用于“任何物品及其构成部分,其生产和分配是(Ⅰ)为卖给消费者……或(Ⅱ)为消费者使用、消费或享受”。不属于该委员会管制的是“烟草及烟草制品;汽车及汽车备件;药物;食品;飞机及飞机部件;某些船艇;以及其他一些物品”——所有这些差不多都属于其它管制机构如酒、烟和火器局、全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联邦航空管理局和海岸警备队等的权限之内。
虽然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刚刚建立不久。但它很可能成为一个主要机构,这一机构对我们行将购买的产品和劳务说来,将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于各种产品,从安全火柴到自行车,从儿童们的玩具火枪到电视接收机,从垃圾箱到圣诞树上的小灯泡,该委员会均进行检验并颁布安全标准。
提高产品的安全性显然是个很好的目标,但将为此付出多大代价,又将按照什么标准来衡量安全或不安全呢?“过大的危险”不能说是一个很科学的词,因为我们无法给它下一个客观的定义。对于儿童(或成年人)的听觉说来,火枪发出多大分贝的声响构成“过大的危险”,我们认为火枪的声响有危险,是因为有时看到训练有素而拿高报酬的“专家”在玩火枪时戴着耳套,这根本不能使纳税人相信他们的钱花得是地方。同不够“安全”的自行车相比,一辆“较安全”的自行车可能速度较慢、较笨重又比较昂贵。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在颁布标准时,根据什么尺度来决定自行车的最大速度和应有的重量,根据什么决定应花更多的钱来达到更大的安全?较安全的标准能带来较多的安全吗?还是只会促成使用者不太注意和不太留神,大部分自行车事故和类似的事故毕竟是由于人们的疏忽大意造成的。
大多数这类问题没有客观的答案——可是,在制定和颁布标准的过程中,这些问题无疑必须加以回答。这种回答将会部分地反映有关公务人员的任意判断,偶尔也反映消费者或消费者组织的评价,他们碰巧对有关产品具有特殊兴趣,然而多半是反映产品制造者的影响。一般说来,只有产品制造者对拟议的标准具有浓厚的兴趣,能够发表有见解的意见。的确,制定产品标准的工作大部分已移交绘了各同业公会。毫无疑问,制定的标准将增进同业公会成员的利益,特别是保护他们不受国内外可能出现的新生产者的竞争。结果将加强现有的国内工厂主的竞争地位,使得研制新产品和改进老产品花费更大,困难更多。
当产品按照事情的正常发展进入市场时,就有机会进行反复的试验。无疑,会生产出劣等产品,会犯错误,会出现意料之外的缺点。但是,所犯的错误通常是小错误——不过也有一些大错误,如最近生产的燧石500号涂料车胎——而且可以慢慢纠正。消费者可以亲自进行试验,看自己喜欢哪些产品,不喜欢哪些产品。
当政府通过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介入时,情形就不同了。在产品得到广泛试用和在实际使用中出差错之前,必须作出许多决定。产品的标准不能适应于不同的需要和爱好。它千篇一律地对待一切需要和爱好。消费者将不可避免地失去试验一系列可供选择的产品的机会。仍然会犯错误,一旦犯错误,就是大错误。
与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有关的两个事例可说明这一问题。
1973年8月,该委员会刚刚成立三个月,“就宣布某些牌子的雾喷粘胶剂具有直接的危险,禁止人们使用。该决定主要是根据某研究机构的一位研究人员的初步发现,这位研究人员认为粘胶剂会使孕妇生下有缺陷的孩子。由于更为彻底的研究无法证实最初的论断,该委员会在1974年3月解除了禁令。”
这样迅速地承认错误是值得大加赞许的,并且对于一个政府机构说来是极其难得的。但最初的决定已经带来了危害。“看来至少有九名使用过雾喷粘胶剂的孕妇,做了人工流产,对该委员会的初步决定作出了反应。她们害怕生下有缺陷的孩子,因而决定停止怀孕。”
一个严重得多的事例是所谓特里斯(Tris)化学药品事件。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成立后,负有实施1953年通过的“易燃纺织品法令”的责任,该法令企图减少因产品、纺织品及有关原料意外燃烧而引起的死亡与伤害。该委员会的前身于1971年颁布了有关儿童睡衣睡裤的安全标准,这一标准在1973年年中被该委员会固定了下来。当时达到这一标准的最经济的方法是把一种名叫特里斯的能防止燃烧的化学药品换进布料中去。不久,在美国制造和销售的儿童睡衣睡裤约99%含有特里斯。后来发现这种化学药物是一种很厉害的致癌物质。1977年4月8日,该委员会宣布禁止在儿童服装方面使用这种化学药品,并且要求从市场上收回用这种化学药品处理过的服装,要求消费者退货。
不用说,该委员会在其1977年年度报告中,并没有承认正是它以前的行动造成了这种危险局面,没有承认它对此应负的责任,而是装出一副面孔,好象是它发现了这一问题,现在正由它来加以解决。最初的要求使千百万儿童面临得癌症的危险。最初的要求和其后禁止使用特里斯,两者都把大量费用强加给生产儿童睡衣睡裤的厂商,归根到底,意味着把费用强加给顾客们。可以说,最终一切费用都要落在顾客头上。
这个例子有助于说明全面管制和市场交易之间的区别。要是当时允许市场发生作用,某些制造商无疑也会使用特里斯,使其产品具有抗燃性,从而增加对顾客的吸引力,但采用特里斯的进程将是缓慢的。在大规模采用这种化学药品之前,人们会发现它的致癌性质,因而停止使用。
环境
环境保护是联邦干预活动发展得最迅速的领域之一。1970年为“保护和改善物质环境”而建立的环境保护局,被赋予日益增大的权力与权限。它的预算从1970年到1978年增加了六倍,现在超过了五亿美元。它拥有大约七千名职员。为了使环境符合它规定的标准,该局每年向工业部门以及地方和州政府征收几百亿美元的费用。目前,在企业新的资本设备净投资总额中,大约有十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用于防止污染。这还未算入由其他机构征收的必要费用,如旨在控制机动车废气的费用,或是土地利用规划或荒地保持的费用,或是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为保护环境而进行的大量其他活动的费用。
保护环境和避免过度污染是现实问题,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当一种行为的全部代价和利益,以及受害者或得益者易于分辨时,市场可以非常有效地确保人们只采取这样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对所有参加者来说,利益大于代价。然而,当代价和利益或者受影响的人不好分辨时,市场就会失灵,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说过,这是“第三方”或毗邻效应造成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某一个住在上游的人污染了河水,他实际上是用脏水去同下游的人交换好水。下游的人很可能愿意根据某种条件进行交换。问题是,不可能使这种交易成为自愿的交易,不可能辨认出谁得到了应由上游某人负责的脏水,而且不可能要求居住在上游的人事先征得居住在下游的人的同意。
政府是一种手段,通过它我们可以弥补“市场的失灵”,可以根据我们的意愿较为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生产出所需要的清洁的空气、水和土地。不幸的是,导致市场失灵的那些因素,也同样使政府难以找到一种满意的解决办法。一般说来,政府同市场参加者相比,前者并不能比后者更容易地辨认出谁是受益者谁是受害者,也不能更容易地估计出上述两种人各得到多少好处受到多少害处。利用政府来补救市场的失灵,常常只不过是以政府的失灵代替市场的失灵。
公众在讨论环境问题时,常常是感情多于理智。在许多讨论中,好象问题是要么有污染,要么没有污染,似乎应该而且可以有一个没有污染的世界。这显然是毫无意义的空想。凡严肃思考过这一问题的人,都不会认为应该使或可以使世界没有污染。我们可以不让汽车污染空气,例如,只消废弃一切汽车就行了。但这却使我们无法享受现在已享有的工农业生产力,从而使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置许多人于死地。大气污染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大家呼出的二氧化碳。我们可以非常简单地终止这一状态。但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正象得到我们需要的其他好东西要付出某种代价一样,得到清洁的空气也是要付出某种代价的。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因而必须权衡减少污染带来的好处和付出的代价。而且,“污染”不是一种客观现象。对一个人来说是污染,对另一个人来说则可能是享乐。对于我们当中某些人来说,摇摆舞音乐是噪音污染;对于我们当中另一些人而言,却是一种享乐。
实际的问题不是“消灭污染”,而是用什么方法能够使污染量“适当”,“适当的”污染量的意思是:减少污染得到的好处刚好大于为了减少污染我们必须放弃其他好东西(如房屋、鞋子、上衣等等)而作出的牺牲。如果我们做得过分,牺牲就会大于得到的好处。
妨碍我们合情合理地分析环境问题的另一个障碍是,人们往往从善与恶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似乎有一些怀有恶意的坏人心肠很黑,是他们把污染物送入大气中的,因而这是一个与动机有关的问题,只要我们当中那些高尚的人愤怒地起来制服这些坏人,一切就会好起来。骂人总是比有理智而艰苦细致地分析问题要容易得多。
就污染说来,被指责的魔鬼往往是“工商企业”,即生产商品和劳务的企业。事实上,对污染负有责任的人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可以说,消费者造成了引起污染的需求。对于从发电厂的烟囱冒出来的烟尘,用电的人是应该负责的。假如我们想得到只带来少量污染的电,我们将直接或间接支付很高的电费,使之足以补偿额外的费用。获得比较清洁的空气、水和其他一切所支付的费用,最终必须由消费者负担。没有人会为此付款。企业只是一种媒介,借以协调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活动。
因为控制污染和保护环境带来的好处和造成的损害往往落在不同人身上,所以问题大大复杂化了。例如,从荒地利用面积的增加,从江河湖泊环境的改善,或者从市内空气污染物的减少等方面得到好处的人,通常和那些因为食品、钢铁或化学制品的成本增加而受到损害的人不是同一类人。我们一般的感觉是:因减少污染而得益最多的人,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教养上,都比因允许较多的污染,从而使物品的成本较低而得益最多的人要强。后一种人宁愿要较便宜的电力,而不要较清洁的空气。董事规则在控制污染方面仍然起作用。
总的说来,政府在控制污染方面采用的方法,同政府在管理汽车运输、管理食品和药物以及增进产品安全等方面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为控制污染,建立了一个拥有处置权力的政府管制机构,该机构颁布了私人企业、个人以及州和地方团体必须遵守的各项规章制度。由上述机构和各级法院确保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
这种控制污染的方法不能有效地确保成本与收益相等。由于完全靠强制命令的方法解决问题,这种方法造成的局面是,谁违反规定谁受惩罚,而不是买与卖;是对与错,而不是多与少。而且,它具有和其他领域中的管制方法相同的缺点。受管制的人或机构卖力去做的,不是花费人力物力达到政府规定的标准,而是对政府官员施加影响,以获得对他们有利的规定。另外,管制人员的自身利益同保护环境的基本目标关系极少。正如官僚统治下的一般情况那样,广为分散的个体利益受到漠视,集中起来的利益则备受照顾。过去,所谓集中起来的利益一般是指商业企业,特别是规模巨大、有权有势的企业。最近,除大企业外,又增加了一些组织得很好、自称代表“公共利益”的集团。这类集团自称代表某些顾客的利益,而顾客可能对它们的存在一无所知。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和现有的专门的管制与监督方式相比,一种有效得多的控制污染的方法是对排出物征收费用,让市场规律起作用。举例来说,可以对排出的每单位废物征收特定数额的税款,而不是要求各厂商建立专门处理废物的工厂,也不是要求它们排入江河湖泊的水必须达到特定的标准。这样一来会刺激厂商采用最经济的方法减少排出物。同样重要的是,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客观地衡量出减少污染的费用。如果低额税率导致污染大量减少,那将明确告诉我们,允许排出污染物几乎得不到什么好处。另一方面,如果征收高额税仍有大量污染物排出,那将表明相反的情形,但高额税将提供足够的金额赔偿受损失的人或者消除损失。税率本身应随着费用和收益的变化而变化。
和管制一样,废物排出税将自动地把费用加到对污染负有责任的产品使用者身上。那些减少污染花费大的产品,相对于减少污染花费小的产品,价格将上升,正如现在那些因管制活动而被征收重税的产品相对于其他产品价格上升一样。前一类产品的产量将上升,后一类产品的产量将下降。废物排出税和管制之间的区别在于:废物排出税将以较低的费用更有效地控制污染,而且给不造成污染的活动带来的负担较少。
A·迈里克·弗里曼第三和罗伯特·H·哈夫曼在一篇出色的文章中写道:“我国不采用经济刺激的方法,是因为该方法行之有效,这样说并非完全开玩笑。”
正如他们所说的,“结合环境质量标准建立污染税制度,会解决有关环境方面的大部分政治冲突,而且将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解决这些冲突,让这一政策的受害者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决定政策的人们力图避免的正是这种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作风。”
上面我们非常简要地论述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影响深远的问题。最后我们指出这样一点也许就够了:在政府根本不应发挥作用的领域中——如在汽车货运、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的价格确定及线路分配中——政府管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在政府应发挥某种作用的领域中也出现了。
建立污染税制度也许还会导致人们重新看待市场机制在某些领域中的作用,在这些领域中,人们一般认为市场机制起的作用是不理想的。毕竟,不理想的市场可能和不完善的政府干得一样好,或者更好一些。在控制污染方面,重新看待市场机制的作用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假如我们看一看现实而不是书本上的词句,那么同一百年以前相比,今天的空气一般说来要清洁得多,水也比较卫生。现在,比起落后国家,在世界先进国家中空气较为清洁,水也较为卫生。工业化产生了新的各种问题,但是它也提供了解决一些重要问题的手段。汽车的发展确实增加了一种污染形式——但它却基本上结束了人们更不喜欢的一种污染形式。
能源部
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美国实行禁运,引起了一连串能源危机,并且,加油站不时发生排长队的现象,从那时起,能源问题一直使我们很伤脑筋。政府的反应是成立一个又一个的官僚机构以控制和管理能源的生产及使用,最后是在1977年成立了能源部。
政府官员、报纸报道和电视台时事评论员,都把能源危机的原因习惯性地归之于贪婪的石油工业,或者浪费的消费者,或者恶劣的气候,或者阿拉伯的酋长们。但实际上,它们对能源危机都没有责任。
石油工业毕竟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期了——并且它一向是贪婪的。消费者不会突然变得浪费起来。我们过去也有严酷的冬天。早在人类有史以来,阿拉伯酋长们就已经在追求财富了。
那些用上述愚蠢的解释来充塞报纸和广播的、精明而老练的人们,似乎从来没有自问过 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1971年以前的一个多世纪中(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为什么没有能源危机,没有汽油短缺,没有关于燃料油的问题。
能源危机是政府造成的,当然,不是故意造成的。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位总统从来没有致函国会要求制定带来能源危机和使人们排长队买汽油的法案。但是既然说到问题的一方面,就得说另一方面。自从尼克松总统1971年8月15日冻结工资和物价以来,政府就对原油、零售汽油以及其他石油产品强行规定了最高价格。令人遗憾的是,取消对所有其他产品的最高价格时,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把原油价格提高了三倍,这阻碍了美国取消对石油及其产品的最高价格。对石油产品规定最高法定价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1971年以来的时期共有的关键性因素。
经济学家们不可能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即如何造成产品过剩和产品不足。你想使产品过剩吗?让政府通过法律规定最低价格,并让这一价格高于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流行的价格。我们曾多次采用这种方法使小麦、食糖、奶油和其他许多农产品过剩。
你想要产品不足吗?让政府通过法律规定最高价格,并让这一价格低于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流行的价格。这就是纽约市以及最近其他城市对出租的住宅做过的事情,并且,这也是所有这些城市正在遭受或即将遭受房荒之苦的原因。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种产品短缺的原因,也是现在出现能源危机和汽油短缺的原因。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在明天结束能源危机和汽油短缺——我们指的是明天,不是今后六个月,不是今后六年。那就是废除对原油和其他石油产品的一切价格管制。
政府的其他错误政策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垄断行为,可以继续使石油产品保持高昂的价格,但不会产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四分五裂、一团混乱的局面。
或许令人惊奇的是,上述解决办法会降低消费者的汽油费用,我们说的是真实的费用。油泵中每加仑汽油的价格可能要上涨几美分,但消费者不用再为排长队和寻找有油的加油站浪费时间和汽油,也不用再为能源部的年度预算付款了。能源部1979年的预算达一百零八亿美元,或每加仑汽油大约九美分。
为什么这种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法没有被采用呢?就我们所见,是由于两个基本原因——一个是一般的原因,另一个是特殊的原因。使每一个经济学家失望的是,要使除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外的大多数人了解价格制度是如何起作用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新闻记者和电视台时事评论员似乎特别反对他们在大学一二年级学过的那些基本原理。其次,废除价格管制会使真相大白,告诉人们能源部二万名雇员的活动是多么无益,多么有害。有人甚至可能会想:要是没有成立能源部该有多好。
卡特总统宣称,政府必须实施一项生产合成燃料的庞大计划,否则到1990年我国的能源将被耗尽。这一主张又怎么样呢?这也是一种神话。政府计划似乎是一种解决办法,这仅仅因为政府处处阻止采用有效的自由市场解决办法。
根据长期合同,我们付给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每桶石油大约二十美元,在现货市场(立即交货的市场)上,我们所付的价格甚至高于此数,可是政府却迫使国内生产者按每桶五点九四美元的低价出售石油。政府对国内生产的石油征税,用以补助从国外进口的石油。我们付给从阿尔及利亚进口的液化天然气的价格,比政府允许的国内天然气生产者所收的价格,要多出一倍以上。政府把严厉的有关环境方面的要求强加给能源使用者和生产者双方,而极少或者毫不考虑经济上所包含的费用。复杂的规章制度和拖拉的官僚作风,大大拖长了兴建以原子核、石油或煤炭为燃料的发电厂所需要的时间,拖长了充足的煤炭供应量进入生产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并且成倍地增加了成本。政府的这种不利于生产的政策,扼杀了国内的能源生产,使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依赖外国的石油——尽管卡特总统说过:“依赖于一条几乎环绕整个地球的、靠不住的油船运输线是很危险的。”
1979年年中,卡特总统提出了一项为期十年、耗资八百八十亿美元的生产合成燃料的庞大政府计划。让纳税人为产自油页岩的每桶石油直接地或间接地花费四十或更多的美元,而同时却禁止国内油井所有者从某些类别的石油中每桶收取五点九四美元以上,这果真有道理吗?或者,象爱德华·J.米切尔在《华尔街日报》(1979年8月27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要问……就算我们花费八百八十亿美元能在1990年生产出一些每桶定价四十美元的合成石油,这又怎么能够使我们不论在今天还是在1990年不依赖石油输出国组织每桶定价二十美元的石油呢?”
从油页岩、含油砂层等等提炼燃料是有意义的,如果把所有的费用都考虑进去之后,这种方法生产能源比各种替代办法更便宜的话。市场是决定上述方法是否便宜的最有效的机制。如果这种方法较为便宜,那么私人企业开发这些替代资源就将是有利的——只要它们获取利益同时负担费用。
只要私人企业相信将来的价格不受管制,它们就可以指望获取利益。否则私人企业就等于是在打一场“反正我都输”的赌。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假如价格上涨,管制及“暴利税”会赫然出现;假如价格下跌,私人企业就要两手空空。这种前景削弱自由市场,并使卡特总统的社会主义政策成为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案。
只要要求私人企业为破坏环境而付款,它们就将负担所有的费用。执行这一政策的方法是对排出物征收捐税,而不是让某一政府机构任意制定各种标准,随后又建立另一个机构来杜绝前一个机构的官僚作风。
对于私人企业发展各种替代性燃料说来,价格控制和管制的威胁是唯一重要的障碍。据说发展替代性燃料风险太大,资本费用太多。这完全错了,冒险正是私人企业的本质所在。把风险强加给纳税人而不是资本家,并不能消除风险。阿拉斯加输油管表明,私人市场可以为有前途的工程筹集巨额资金。打发税务员征税,并不能增加国家的财力,增加国家财力的方法是让证券市场发挥作用。
不管怎么说,我们人民将要为我们所消费的能源付钱。假如我们直接付钱,并能够自己决定怎样使用能源,而不是通过纳税和通货膨胀间接付钱,也不是由政府官员告诉我们怎样使用能源,那么,我们为所消费的能源支付的总金额将会少得多,得到的能源将会多得多。
市场
这个世界不是尽善尽美的。永远会有质量低劣的各种产品、庸医和诈骗能手。但总的看来,如果允许市场竞争起作用,那它同强加到市场头上的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相比,将能更好地保护消费者。
正象亚当·斯密在本章开头我们引用过的那段话中所说的,竞争保护消费者不是因为商人比官僚们心肠软,不是因为商人有更多的利他主义思想,或更慷慨大方,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有才能,而只是因为为消费者服务正是为他们自己的私利服务。
假如一个店主向你出售的商品比其他店主出售的商品质量低或价格高,你就不会继续光顾他的商店了。假如他买来供出售的商品不合你的需要,你就不会购买。因此,商人们在全世界搜购可能适合你的需要并受你欢迎的各种产品。而且他们极力推销购买来的商品,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会垮台。你走进一家商店,没有人强迫你买什么。你可以随便买哪一样东西或者到另一家商店去。这是市场和政治机构之间的基本区别。你能自由选择。没有警察从你口袋里掏钱去为你不想要的某样东西付款,没有警察要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
然而,鼓吹政府管制的人会说,如果没有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怎么能阻止企业出售搀了假的或者有危险的产品呢?正如特效磺胺、撒利多迈德以及其他许多不太为人所知的事故所表明的,出售这类产品代价是非常高昂的。这是一种非常卑劣的做生意的手法——不是招揽忠实而可靠的顾客的方法。当然,如果没有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会出现各种差错和事故,但正如特里斯事件所表明的,政府管制并不能阻止事故的发生。区别在于犯严重错误的私人企业可能垮台,而犯严重错误的政府机构则很可能因此而得到更多的预算。只要无法预测不利情况的出现,就肯定会出现一些差错和事故,但同私人企业相比,政府并没有更好的方法来预测不利情况。防止差错和事故的唯一方法是停止前进,但停止前进也就消除了出现意想不到的有利情况的可能性。
鼓吹政府管制的人还会说,没有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消费者怎么能判断各种复杂的产品的质量呢?市场的回答是消费者无须自己作出判断。他有一些可以依赖的对象,其中之一就是中间人。例如,百货公司的主要经济职能是根据我们的利益检查质量。我们购买的东西很多,一个人不可能对所有东西都懂行,即便是衬衫、领带或鞋子等最平常物品,我们有时也不能正确地判断其质量。如果我们买了一件不好的东西,我们多半会退给出售商品的零售商,而不会退给工厂主。在判断产品质量上,零售商所处的地位远比我们优越。同百货公司一样,娄巴克·西尔斯公司和蒙特文梅里·沃德公司不仅是销售机构,而且是为消费者有效地检验和证明产品质量的机构。
另一种可以依赖的市场手段是商标的声誉。通用电气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都要获得生产安全可靠的产品的声誉。这是它们“信誉”的源泉,作为一家公司这种信誉甚至比厂房设备更有价值。
还有一个手段是私人检验组织。这样的检验组织在工业部门中是很普遍的,并在证明大量产品的质量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消费者来说,有象消费研究会一类的私人组织,该研究会创立于1928年,并仍在它每月出版的《消费研究》杂志上评价各种各样的消费品;还有1935年建立的消费者联合会,它出版《消费通讯》。
消费研究会和消费者联合会都很成功,有充足的资金雇用大批人员,其中包括工程师以及经过训练的检验人员和办事人员。可是,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它们至多只能吸引1%或2%的可能的追随者。这两个组织中规模较大的消费者联合会现在拥有大约二百万名会员。它们的存在是市场对消费者需求的一种反应。它们的规模很小,而且没有出现其他类似的机构,这表明只有少数消费者需要这类机构,并愿意为它们提供的服务付钱。大多数消费者一定正在从其他方面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指导,并愿意为此支付费用。
有人宣称消费者会被广告牵着鼻子走,这一论断怎么样呢?正如许多耗资巨大的广告宣传的可耻失败所表明的,我们的回答是消费者不会被广告牵着鼻子走。埃德塞尔牌汽车是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一种最不受欢迎的汽车,但该公司却开展大规模的广告宣传运动推销这种汽车。从根本上说,广告是做生意的一种成本,企业家都想从付出的钱中得到最大的好处。设法满足消费者真正的需要和愿望,比起试图制造人为的需要和愿望,不是更为合理吗?的确,同制造人为的需要相比,向消费者出售满足他们现有需要的商品,一般是比较便宜的。
一个极好的例子是所谓人为制造出来的要求改换汽车型式的愿望。可是,尽管开展了耗资巨大的广告宣传运动,福特汽车公司终究没能使埃德塞尔牌汽车成为畅销货。市场上总是有一些不经常改换型式的小汽车,如美国制造的苏珀巴牌小汽车(这种汽车是奇克牌出租汽车的仿制品)以及许多外国小汽车,但它们所能吸引的顾客一直不过是很少的百分之几而已。如果不经常改换型式的汽车是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则制造这种汽车的公司就会兴旺起来,同时其他公司也会仿效它的做法。多数批评家反对广告宣传,不是因为广告宣传操纵嗜好,而是因为一般公众具有浮华庸俗的嗜好——即同批评不一致的嗜好。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光凭想象下结论,应该对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进行一番比较。即要货比货。如果商业广告是骗人的,那么,不要广告或者政府对广告加以控制,是否更为可取呢?至少私人商业方面有竞争,你登广告,我也可以登广告,而一牵涉到政府,就比较难于做到这一点了。政府也从事广告宣传。政府拥有数以千计的与公众联系的代理人,他们用最动听的语言介绍政府的产品。同私人企业的广告宣传相比,政府的广告宣传更加骗人。我们只要看一看财政部为出售其储蓄债券进行的广告宣传就够了。美国财政部为了出售储蓄债券特地印制了一种宣传卡片,由各家银行分发给广大顾客,上面印有以下引人进行储蓄的话:“美国储蓄债券……多么伟大的储蓄方式!”可是,在过去十几年里,凡购买储蓄公债的人都上了当。他在公债到期所得到的金额,同他购买公债所付出的金额相比,只能购买较少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他还得为不利的“利息”纳税。所有这一切是通货膨胀造成的,而通货膨胀则是向他出售债券的政府造成的。然而,财政部却继续散发上述宣传卡片,为储蓄债券做广告,宣称储蓄债券可以“增进个人安全”,是“自行增值的礼物”。
有人说垄断的威胁导致了国会颁布各项反托拉斯法令,这种说法怎么样呢?垄断的确是一种威胁。消除这种威胁的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在司法部下面设立更为庞大的反托拉斯机构或者给联邦贸易委员会拨更多的款。而是废除阻碍国际贸易的各种现有的关卡。这样,来自全世界的竞争将比各项反托拉斯法令更有效地削弱国内的垄断。英国的弗雷德·莱克无须从美国司法部取得帮助以破坏航空公司的卡特尔。日本和西德的汽车制造商迫使美国的汽车制造商生产较小型的轿车。
对消费者的最大威胁是垄断——不论是私人的还是政府的垄断。保护消费者的最有效方法是国内的自由竞争和遍及全世界的自由贸易。要想使消费者不受单一的卖主的剥削,就必须有另外的卖主,消费者能向他购买,而他也渴望卖东西给消费者。在保护消费者方面,可供选择的供应来源要比全世界所有的拉尔夫·纳德之流有效得多。
结论
“流泪的日子即将过去。贫民窟将只是昔日的回忆。我们将把牢房变成工厂,使监狱变成仓库和粮仓。男人将挺起胸膛,妇女将面带微笑,孩子将又蹦又跳。地狱将一去而不复返。”
著名的福音传教士和禁酒运动的领导人比利·森代,就是以上面一段话迎接1920年禁酒运动的开始的。这场运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人们突然发现真正的道德标准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它清楚地告诉我们,目前的道德觉醒,即目前开展的保护大家不受自身侵害的运动将向何处发展。
禁酒运动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开展起来的。酒是一种危险物。每年饮酒过度而丧生的人数,往往超过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管制的所有危险物毒死的人数。但是,禁酒运动究竟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结果是谁喝酒谁就犯有违反国家法令罪,而不得不建造新的牢房和监狱收容罪犯。艾尔·卡彭及巴格斯·莫兰得以横行一时,他们谋财害命,敲诈勒索,抢劫禁卖的酒,并且非法酿酒卖酒。那么,谁是他们的顾客?谁买他们非法供应的酒呢?一些令人尊敬的公民买他们的酒,他们虽然决不会赞同或参与艾尔·卡彭及其同伙干的那种罪恶勾当,但他们却想喝一点酒。为了喝上一点酒,他们不得不违反法律。禁酒运动没有能阻止人们饮酒。它只是使许多在其他方面遵纪守法的公民变成了违法者,给饮酒这件本来很平常的事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从而吸引了许多青年人。它压制了许多具有制裁作用的市场力量,这些力量通常可以保护消费者不受质量低劣的、弄虚作假的以及有危险的产品的损害。它腐蚀了监狱看守,并使道德风尚败坏。它并没有阻止酒的消费。
在禁止使用环己基氨基磺酸盐、滴滴涕和莱特里尔方面,我们目前还远远没有造成上面那种状况。可是,我们正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在被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禁止出售的药物方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半黑市;人们已开始到加拿大或墨西哥购买他们在美国不能合法买到的药品,正象禁酒运动期间人们为了得到一点合法的酒所做的那样。许多认真负责的医生感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要么使用解除病人痛苦的药品而违反法律,要么不使用这种药品而严格遵守法律。
如果我们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最终将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政府有责任保护我们不受危险物的侵害,那么根据逻辑推理,势必要禁止人们饮酒和吸烟。如果应该由政府保护我们在骑自行车和玩火枪时免遭危险,那么根据逻辑推理,势必要禁止悬式滑翔、骑摩托车和滑雪等更加危险的活动。
甚至主管各管制机构的人想到这种前景,也会不寒而栗。就我们其余的人说来,公众对于控制我们行为的更为极端的尝试——如要求汽车安装连锁安全装置以及提议禁止生产糖精等——的反应,充分证明我们丝毫也不需要这种政府控制。假如政府真的掌握一般人无法得到的、有关我们咽下的东西或我们从事的活动的优缺点的情报,那政府应该提供给我们这方面的情报。但政府最好还是听任我们自由选择,让我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本节内容概述
假如政府真的掌握一般人无法得到的、有关我们咽下的东西或我们从事的活动的优缺点的情报,那政府应该提供给我们这方面的情报。但政府最好还是听任我们自由选择,让我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纠正外部性的公共政策:
可交易的许可证如排污
License tradable
治污成本最低的企业会承担最大的减排份额
拍卖许可证
第8章 谁在保护工人
过去两个世纪里,在美国和其他经济上先进的社会里,普通工人的状况有了极大改善。今天,在上述社会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人从事那种繁重不堪的劳动,这种劳动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是常见的,而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现在仍然是不足为奇的。工作条件得到了改善;工作时间也缩短了;享受假期和其他小额优惠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收入大大增加,使普通家庭得以享有早些时候只有少数富人才能享有的生活水平。
如果进行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向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促使全体工人状况得到改善的原因是什么?”多数人的回答很可能是“工会”,其次是“政府”——尽管作出“没有任何原因”或“不知道”或“没看法”的回答的人也许比前两种人要多。可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证明,这些回答都是错误的。
在大部分时期中,工会在美国并不重要。直到1900年,全体工人中只有3%是工会会员。甚至在今天,工会会员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仍然不到四分之一。很显然,工会不是促使美国全体工人的状况得到改善的主要原因。
同样,在“新政”以前,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是最低限度的。政府所起的必不可少的作用,是保护自由市场的正常活动。但是,很显然,直接的政府行动不是促使全体工人的状况得到改善的原因。
至于有人说工人状况的改善“没有任何”原因,当前工人的状况正好证明这样回答是错误的。
工会
滥用语言的最惊人的事例之一是把“劳方”看作是“工会”的同义词——例如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词句:“劳方反对”某某提案,或“劳方”的提案如何如何。这是双重的错误。首先,在美国四分之三以上的工人不是工会会员。甚至在英国,那里的工会长期以来远比美国的工会强大,大部分工人也不是工会会员。其次,把“工会”的利益及其成员的利益等同起来是错误的。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多数工会与其成员的利益是有联系的,而且联系密切,但有许多事例表明,工会头头常常利用合法手段或非法手段如滥用和私吞工会基金,牺牲工会会员的利益而为自己谋私利。这警告我们不要不自觉地把“工会”的利益同“工会会员”的利益等同起来,更不用说把工人整体的利益与工会的利益等同起来。
语言的这种滥用现象是由于过高估计工会的影响和作用而产生的。工会的行动是看得见的,并且是有新闻价值的。它们常常成为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晚间的电视节目也常常不加删节地加以报道。而决定美国大多数工人工资的“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亚当·斯密语),则不那么容易被人看到,也不大引起注意,其结果是讨价还价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
语言的上述滥用也导致了这样的信念,即工会是现代工业发展的产物。事情决非如此。实际上,工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以前的时期,追溯到封建时期城市和城邦内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特有组织形式,即行会。的确,现代工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更为遥远的年代,追溯到大约二千五百年前希腊的医生之间达成的协议。
公认的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于西元前460年左右出生在希腊的科斯岛上,该岛距离小亚细亚海岸只有几英里之遥。当时,科斯岛是一个繁荣的岛屿,已经是医学中心。在科斯岛上研究医学之后,希波克拉底遨游远方,他作为医生,特别是因为他消灭瘟疫和流行病的本事,逐步树立了崇高的声望。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回到科斯岛,在该地他创立并主管了一所医学院和一个医疗中心。他教导所有希望学习的人——只要他们付学费。他的医疗中心在希腊全境出了名,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病人和医生们。
当希波克拉底于一百零四岁(这完全是根据传说)去世时,科斯岛到处都是行医的人,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是他的门徒。争夺病人的竞争是激烈的,因而毫不奇怪,必须采取一致的行动来解决有关竞争的问题——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使医生的行为“合理化”,以便消灭“不公平的竞争”。
所以,在希波克拉底去世大约二十年以后(这也是根据传说),医生们聚集到一起创立了行为守则。他们以自己老师的名字给守则命名为希波克拉底誓约。此后,在科斯岛上并日益遍及世界其他地方,每一个新培训的医生,在他开业之前,都要宣誓忠于上述誓约。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美国已成为大部分医学院校毕业典礼的一部分。
象大多数职业法规、商业交易协定和工会合同一样,希波克拉底誓约充满了帮助病人的美好理想:“我将用自己的力量,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和判断力解除病人的痛苦。……无论来到哪一家,我都要帮助病人解除痛苦,而决不存心做损害或伤害人的事情。……”等等。
但是,该誓约也包含着一些同上述精神不相符的内容。例如誓约上有这样的话:“我将把医术、讲稿和所有其它学问传授给我的儿子、我师傅的儿子以及受过正式训练并宣过誓的人,而不传给别人。”今天,我们也许会把这称作封闭式雇用制度(即只雇用某一工会会员的制度)的前身。
誓约还提到了患有肾结石或膀胱结石的病人,原话是这样的:“哪怕是结石病,我也决不动手术,我将交给具有这种技能的医生来处理此事。”这可以说是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划分市场的极好协议。
我们猜想,当医学院的毕业班宣誓时,希波克拉底在九泉之下定然不得安宁。当年,他曾经把知识传授给每一个对医学感兴趣并且愿意交付学费的人。他可能会强烈反对那种划分市场的做法。自从制定出希波克拉底誓约到今天,全世界的医生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竞争的危害,一直采用了这种做法。
美国医学协会很少被看作是工会,人们认为它的作用远远超出了普通工会的范围。它向其会员及整个医学界都提供重要的服务。然而,它实际上是工会,而且我们认为,是我国最成功的工会之一。几十年来,它缩减了医生人数,抬高了医疗费用,同时阻止了来自外行业的人同“受过正式训练并宣过誓的”医生们相竞争——自然,这一切在名义上都是为了帮助病人。关于这一点,本书无须重复的是,医学界领导人确实真诚地相信,限制从医人数对病人有好处。现在,我们大家已逐步熟悉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为自己谋福利就是为社会谋福利。
随着政府在医疗事业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且承担越来越多的医疗费用,美国医学协会的势力日趋衰落。另一垄断集团即政府官僚集团正在取代它。我们认为,这种结果部分地是由该协会本身采取的行动造成的。
医疗事业方面的这种发展趋势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未来将得到什么样的医疗以及为此将付出多少费用可能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本章讨论的是工人。不是医疗事业,因此我们只讨论与工会有关的医疗事业方面的一些经济问题,从而说明运用于所有工会活动的原理。我们将把医疗事业目前遇到的其他一些重要而使人迷惑不解的各种问题暂且放在一边。
谁得到了好处?
医生在美国属于享有最高报酬的劳动者。这种状况对于已经从工会得到好处的人们说来并不是例外情况。尽管人们经常得到的印象是,工会保护低工资工人免受雇主的剥削,但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最成功的工会总是这样一些工会,其会员从事的职业需要熟练的技能,不论有没有工会,他们的工资都比较高。这类工会只是使本来已经很高的工资更高。
例如在美国,航空公司驾驶员每周工作三天,1976年他们的平均年薪是五万美元,而且这以后又有相当大的提高。在一份题为“航空公司驾驶员”的研究报告中,乔治·霍普金斯写道:“今天飞机驾驶员惊人的高薪金,与其说来自他们承担的责任或他们掌握的技术,不如说来自他们通过工会获得的受到保护的地位。”
在美国,最老的传统工会是行业工会,如木匠、水管工、泥水匠等工人组织的工会,他们同医生一样,也是技术熟练、工资较高的工人。最近,发展最快的工会——而且的确几乎是唯一有所发展的工会——是政府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中小学教师、警察、卫生工作者以及其他各种政府雇员)组织的工会。纽约市的市政工人工会,通过把该城市推到破产的边缘显示了它们的力量。
中小学教师和市政雇员的情况,说明了一条在英国已经清楚地得到了证明的一般原理。他们的工会不直接同支付他们会员薪金的纳税人打交道,而同政府官员打交道。纳税人和工会与之打交道的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愈松弛,政府官员和工会相互勾结牺牲纳税人利益的趋势就愈益加强——这是某些人把另一些人的钱用之于第三者身上的另一个例子。这就是为什么纽约等大城市中的市政工人工会比小城市中的市政工人工会强大的原因,同时也是随着政府对学校活动和教育经费的控制日益集中化,日益脱离地方政府,中小学教师的工会越来越强大的原因。
同美国相比,英国政府对更多的工业部门实行了国有化,其中包括煤炭工业、公用事业、电话和医院。在英国的国有化工业部门中,工会一般特别强大,劳资问题也最为严重。同样的因果关系也反映在美国邮政工人工会的力量中。
假定强大的工会的会员工资比较高,明显的问题就是:是因为工会强大,会员们才得到高工资呢;还是因为会员的工资高,工会才强大?为工会辩护的人宣称,会员的高工资可以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而且,一当全体工人都是工会会员时,所有工人都将领取高工资。
然而情况是复杂得多的。极为熟练的工人的工会无疑地能提高其会员的工资;可是,不论怎样都会得到高报酬的人,在组织强有力的工会方面是处于有利地位的。而且,工会提高某些工人工资的能力,并不意味着普遍实行工会制度会提高全体工人的工资。正好相反,这是产生误解的根本原因,强大的工会能为其会员赢得利益,首先是靠牺牲其他工人的利益。
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是了解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即需求法则:某种东西的价格愈高,愿意购买它的人就愈少。使某种劳动较为昂贵,这种劳动提供的工作机会就会减少。使木匠活较为昂贵,则建造的房屋减少,并且所造的这些房屋会采用木匠活不多的建筑材料和方法。提高航空公司驾驶员的工资,乘飞机旅行将变得更贵。乘飞机的人将会减少,因此对于航空公司驾驶员来说就业机会也会少一些。反过来说,减少木匠、飞机驾驶员的人数,他们就会得到较高的工资。缩减医生的人数,他们就能收取较高的酬金。
一个成功的工会可以减少它所控制的工作机会。其结果是,希望按照工会的工资标准获得这类工作的某些人,就不会达到目的了。他们被迫转向别处。更多的工人会寻找其他工作,压低了这些工作的工资。普遍组织工会不会改变这种局面。这对于找到职业的人意味着高工资,与此同时,对于其他人则意味着更多的失业。更为可能的是,会出现一些强大的工会和弱小的工会,强大工会的会员会象现在这样,在损害弱小工会会员利益的情况下得到较高工资。
工会领导人经常说可以通过减少利润来提高工资。这是不可能的:根本没有富余的利润来提高工资。美国的全部国民收入目前约有80%用于支付工资、薪金和小额优惠。余额的一半以上用于支付租金和贷款的利息。公司利润——这是工会领导人常常提到的——总额不到国民收入的10%。这还是纳税前的利润。纳税以后,公司利润大约是国民收入的6%。即使全部利润都投放进去,也几乎不可能使所有人都领高工资。而且,这不啻于杀鸡取蛋。最低限度的利润,为投资于工厂和机器以及发展新的产品和新的方法,提供了刺激。这种投资和这些革新,近几年来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率,并为高而又高的工资准备了必要的资力。
提高某些工人的工资必然损害其他工人。将近三十年以前,我们当中有人曾经估计,在我国平均约有10-15%的工人,通过工会或者类似美国医学协会这样的组织,得以使他们的工资比在没有工会的情况下多提高了10-15%,而另外85—90%的工人挣得的工资则因此而减少了大约4%。最近的研究表明,现在的情况大体上仍然是这样。高工资的工人工资越来越高,低工资的工人工资越来越低。
我们所有的人,包括由工会高度组织起来的人们,作为消费者,由于工会会员的高工资对消费品价格的影响而间接地受到损害。对于包括木匠在内的每一个人说来,房屋的售价太高了。工会阻挠工人运用他们的技能生产价值最高的东西,工人被迫从事那些生产率较低的活路。对于我们全体说来,可得到的物品的总量,比应有的数量要少。
工会力量的来源
工会为什么能够提高其会员的工资?工会力量的基本来源是什么?回答是:工会可以缩减可得到的就业机会,换言之,可以缩减适于从事某类工作的人数。通常在政府协助下,用实行高工资率的办法,工会得以缩减就业机会。同样在政府协助下,主要是通过发给许可证的方式,工会得以缩减合用者的人数。工会偶尔还同雇主相勾结,对其会员所生产的产品实行垄断,以这种办法来增加其力量。
实行高工资率。如果工会可以设法使承包人支付给水管工或木匠的工资不少于,比如说每小时十五美元。那将会减少这方面的就业机会。当然,这也将增加愿意从事这类工作的人数。
假定目前可以实行这种高工资率。那么,必须采取某种办法来在寻求这种有利可图的工作的人们中间分配有限的就业机会。已采用过的许多方法包括:搞裙带关系,即把工作保留给家庭成员;按照资历和学历招工;超额雇用工作所需要的人员,即随便安排工作;以及不折不扣的行贿受贿。由于牵扯到很多利害关系,因而采用哪种方法对于工会来说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某些工会不允许在公开会议上讨论有关资历方面的规定,因为这种讨论常常引起殴斗。为了优先获得工作而向工会官员们付酬金,是一种普通的行贿形式。工会采取的种族歧视措施虽然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但仍然是分配工作的另一种方法。如果申请工作的人过多,供分配的工作有限,则招工方法必定是武断的。用偏见及类似的不合理的方法来解决把谁关在门外的问题,这种做法常常得到“已入会者”的大力支持。种族和宗教歧视也渗入到了医学院校的入学方面,原因同上面一样,即可接受的申请者过多,因而需要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
让我们再来看工资率,工会采用什么方法实行高工资率呢?一种方法是采取暴力行动或以暴力相威胁:宣称如果雇主雇用非工会会员,或付给工会会员的工资低于工会指定的工资率,将毁坏雇主的财产或者殴打他们;宣称如果工人同意为较低的工资干活,就揍他们或破坏他们的财产。这就是工会在进行工资调解和谈判时,为什么经常伴随有暴力行为的原因。
一种更为容易的方法是取得政府的帮助。正因为这个缘故,工会都把总部设在华盛顿美国国会的附近,而且在政治活动上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霍普金斯在有关航空公司驾驶员工会的研究报告中特别提出:“该工会得到了联邦立法的充分保护,使职业航空公司驾驶员实际上成了受国家保护的人。”
政府帮助建筑工人工会的主要形式是戴维斯-培根法案,该联邦法令规定,凡是同联邦政府签订有价值二千美元以上合同的承包人,支付的工资率不得低于有关地区由劳工部长决定的“同等工人和技工普遍享有的”工资率。实际上,“在决定工资的绝大多数场合……不论建筑面积和种类如何,普遍享有的工资率”往往被规定为工会的工资率。后来,这一有关工资率的条款写进了其他许多有关联邦政府援建项目的法令,写进了三十五个州(截至1971年)颁布的有关建筑开支的法令,从而扩大了上述法案涉及的范围。实施这些法令的结果是,政府对于大量建筑活动实行了工会的工资率。
甚至使用暴力暗中也包含有政府的支持。一般说来,在劳资争议中公众是同情工会的,这导致了政府当局容忍在其他情况下决不会容忍的行为。在劳资争议中,某人的小汽车被推翻,工厂、商店或住家的窗子被捣毁,甚或有人遭到殴打并严重受伤,肇事者不大可能被罚款,更不用说去坐牢了,但如果在其他情况下发生同样的事情,情形就不一样了。
政府实行工资率的另一套措施是最低工资法令。颁布这些法令据说是为了帮助低收入者。其实,它们损害了低收入者。要求颁布最低工资法令的压力,来自那些在国会面前作证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人。这些人不是贫苦人民的代表。他们主要是劳联-产联以及其他劳工组织的代表。在这些工会中,没有一个会员挣得的工资接近法定的最低工资。尽管有一套关于帮助穷人的漂亮话,但他们主张提高最低工资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其工会的会员免受竞争的危害。
最低工资法令要求雇主们歧视技术低的人。没有人这么明说过,但事实确实是如此。且以受教育很少而没有什么技能的青少年为例,其劳务比如说每小时仅值二美元。他或她也许渴望为这种工资干活,为的是掌握较多技能,从而得到较好的工作。但最低工资法令宣称,只有雇主愿意付给他或她(在1979年)每小时二点九美元,这样的人才能受雇。也就是说,除非雇主愿意仁慈地把九十美分加到青少年劳务所值的二美元上面,否则他们是不会被雇用的。青年人因不能得到每小时二点九美元而失业,反而说这种境况比接受每小时二美元的工资而就业要强些,这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青少年特别是黑人青少年的很高的失业率,既是一种耻辱,又是社会动乱的一个严重根源。青少年失业率的增加主要是最低工资法令造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低工资是每小时四十美分。战时的通货膨胀曾使这个数目低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可言。此后最低工资急剧上升,1950年升至七十五美分,1956年上升到一美元。五十年代初期,全体工人的失业率大约为4%,青少年的失业率平均为10%——对于刚加入劳动大军的人们说来,10%的失业率也许比人们预料的稍微高了一些。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大致相等。在最低工资率急剧提高之后,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扶摇直上。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在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之间出现了差距。目前,白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在15-20%之间,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在35-45%之间。我们认为,在所有法令中,最低工资率法令是最歧视黑人的一项法令。政府先是开办中小学,其中许多青年人,特别是黑人青年,所受的教育很差,以致他们未能掌握必要的技能从事工资较高的工作。随后政府再一次惩罚了他们,阻止他们为了得到在职训练而为低工资干活。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帮助穷人的名义下进行的。
限制人数。实行工资率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限制可能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数。当雇主众多,难于实行某种工资率时,这种方法是特别有吸引力的。医疗事业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某工会的大量活动是以限制开业医生为目的的。
正象实行工资率一样,要想在限制人数方面获得成功,通常需要政府的帮助。在医疗事业中,发放医生开业许可证是关键问题:凡想要“行医”的人必须得到政府的许可。不用说,只有医生有可能被认为有能力判断医生候选人的资格,因此各州(在美国,发放许可证的工作在州政府的管辖权限之内,联邦政府不管此事)签发执照的部门通常由清一色的医生组成,或者医生占优势,这些医生一般又是美国医学协会的会员。
上述主管部门或州的立法机关提出了批准许可证的各项具体条件,实际上是让美国医学协会来左右获准开业的人数。条件包括:必须受过长期的训练,必须毕业于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并在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医院担任过实习医生。绝非偶然,“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和医院的名单,一般是与美国医学协会的医学教育和医院委员会公布的名单完全相同的。任何学校如不得到美国医学协会的医学教育委员会的批准,是建立不起来的,或即使建立起来,也不能维持很久。得到批准有时需要按照该委员会的意见限制医生人数。
在经济压力特别大的三十年代萧条时期,有组织的医学界显示了限制从医人数的巨大力量。尽管当时从德国和奥地利(那时都是先进医学的中心)涌入了大批受过严格训练的难民。但希特勒上台后的五年中,获准在美国开业的外国医生,并不比前五年多。
营业执照的发给被广泛用来限制各种职业的从业人数,特别是医学等职业的从业人数,在这类职业中有许多单个的开业医生,他们同大量的个别主顾打交道。象在医学中一样,主管发放执照的部门,主要是由该行业持有营业执照的成员组成——不论他们是牙医、律师、整容专家、航空公司驾驶员、水管工,还是殡仪业者。没有哪个职业如此冷僻,以致无须用发给执照的办法来限制从业人数。据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说:“在某州议会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各职业集团纷纷要求发给执照,其中有拍卖人、采矿者、房屋改建承包商、宠物饲养人、电学家、性病医生和性生活顾问、数据处理者、估价人以及电视机修理人。夏威夷州签发文身艺术家执照。新罕布什尔州签发避雷针推销员执照。”签发各种执照的理由总是一样的:保护消费者。然而,要发现真正的理由,我们得看一看在各州议会里是谁在为实行或巩固营业执照制度进行游说。游说者一律是有关从业人员的代表,而不是顾主的代表。千真万确,水管工也许比其他任何人更清楚地知道如何保护他们的顾客。然而,当水管工在背后竭力谋取合法权力以决定谁可以当水管工时,就难以把他们对顾客的利他主义的关心看成是主要动机了。
加强对本行业就业人数的限制,同时增加领有执照的开业者的业务,各有组织的职业集团总是千方百计使其业务活动范围规定得尽量宽一些。
通过签发执照限制从事各种职业的人数,其结果之一是创造出了一些新学科:例如在医学中出现了整骨术及脊柱按摩疗法,这些医疗科目试图采取发给执照的办法,限制其人数。美国医学协会已提出许多诉讼,指控一些脊柱按摩医生及整骨医生非法开展其他医疗业务活动,企图把他们限制在尽可能狭小的营业范围之内。而脊柱按摩医生和整骨医生则控告其他医生没有得到执照就实施脊柱按摩疗法和整骨术。部分地由于新的高度精密的手提设备的出现,最近在各类居民区中发展起一种新的保健服务项目,即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提供急救服务。这类服务有时由市政府或市政府的一个机构提供,有时由不折不扣的私人企业提供,这类机构的人员主要是医务辅助人员,而不是持有执照的医生。
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一个附属于城市消防队的上述私人企业的老板乔·多尔芬,描述该企业的效能如下:
在我们服务的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地区,这是一个拥有五十八万人口的县,在提供急救服务以前,因心脏病突然发作而心脏停止跳动的病人,通过住进医院而活过来并且病愈出院的不到1%。提供急救服务以后,仅在头六个月中,23%的心脏停止跳动的病人被成功地救活了,他们病愈出院并且回到了社会生产岗位上。
我们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实说明了一切。然而,说这同医学界有关系有时是很困难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更为一般地说,导致工人停工一个最经常的原因,是所谓管辖范围争议,即有关各职业业务活动范围的争议。曾采访过我们的一个广播电台记者,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他强调采访要短,以便在他的盒式录音机的录音带上只录一面。翻录音带的工作必须留给电工工会的一个会员去做。他说,如果他自己把它翻过来,当他回到广播电台时,录了音的磁带会被洗掉,采访就白费了。这种行为正同医生反对辅助医务人员提供急救服务一样,并且其动机也是一样的:增加对一个特殊集团的服务的需求。
工会和雇主的勾结。工会有时通过帮助工商企业联合起来规定价格或者分配市场来增强自身的力量,而规定价格或者分配市场等活动在反托拉斯法令条件下对工商企业说来是违法的。
从历史上说,三十年代的采煤业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事例。当时的两个格费伊煤炭法案试图为煤矿经营者共同规定价格的行为提供法律上的支持。当三十年代中期第一个法案被宣布为违反宪法的法案时,约翰·L.刘易斯以及他所领导的美国矿工联合会挺身担负起了重担。每当开采出来的煤炭量多到似乎将迫使价格下跌时,刘易斯就与采煤工业进行默契般的合作,通过号召罢工或停工,控制产量并从而控制价格。正如一个煤业公司的副董事长在1938年指出的:“他们(美国矿工联合会)已做了大量事情来稳定烟煤工业,并尽力使该工业能够继续盈利。虽然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但实际上他们按上述方式所作的努力……比起煤矿经营者自己的努力……要稍许更加有效一些。”
利益在经营者和矿工之间被瓜分了。矿工得到了高工资,这自然意味着更多的机械化和较少的矿工被雇用。刘易斯明确承认这种结果,并且更愿意接受这种结果——他把受雇的矿工的高工资看成是对受雇人数减少的一种充分补偿,假如受雇者都是该联合会会员的话。
矿工联合会之所以可以起这种作用,是因为工会不受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限制。利用这一便利条件从事非法活动的工会,与其说是工人组织,倒不如说是出售使整个行业卡特尔化的劳务的企业。卡车司机联合会也许是最受人注意的工会。关于詹姆斯·霍法以前的卡车司机联合会主席戴维·贝克(两人都已入狱),有一个或许不足凭信的故事。当贝克与华盛顿州的各啤酒厂就啤酒厂卡车司机的工资进行谈判时,他被告知他所要求的工资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东部啤酒”的价格会因此而低于华盛顿州的啤酒价格。他问东部的啤酒应该是什么价格,才能接受他要求的工资。有人回答说,东部啤酒每箱的价格应该是X美元。据说他当时许下愿:“从今后东部啤酒每箱的价格保准会变成X美元。”
工会可以而且的确经常为其会员提供有用的服务,例如:就会员的就业条件同雇主进行谈判,反映会员的疾苦,以及使会员感觉到有所依附,有所作为。作为自由的信仰者,我们赞成给予人们最充分的机会,自愿组织工会,并且认为工会可以提供会员所希望并愿意为此出钱的任何服务,只要工会尊重其他人的权利而且不使用暴力。
然而,工会以及职业协会等组织,并没有依靠严格自愿的活动和全体会员来达到其公开宣布的主要目标,即提高会员的工资。工会及类似的组织在使政府给予它们特权与豁免权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些特别权利使他们在牺牲其他工人和全体消费者利益的条件下,得以让它们的某些会员和官员受益。总的说来,受益者的收入要比受害者的收入高许多。
政府
除了保护工会会员之外,政府还通过了旨在一般地保护工人的大批法令:向工人提供补偿费的法令,禁止雇用童工的法令,规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法令,建立保证实行公平就业的各种委员会的法令,促进积极行为的法令,建立调节就业的联邦安全和卫生管理局的法令,以及其他不胜枚举的法令。
某些措施对工作条件的改善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大多数法令,如工人补偿费法令和童工法,在它们颁布以前,就已体现在人们的自觉行动中了,颁布这些法令也许只是对边远地区具有实际意义。其他法令,你知道后不要感到惊奇,既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害处。它们在减少普通工人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同时,却为某些工会和雇主提供了权力的来源,为官僚们提供了官职的来源。安全和卫生管理局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是一个可怕的官僚主义机构,人们已对它怨声载道。正如最近流传的一个笑话所说: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你知道需要多少美国人安一个电灯泡吗?另一个人回答说:需要五个人,一个人安灯泡,四个人填写环境影响报单以及安全和卫生管理局要求的各种报告书。
政府确实在很好地保护一类工人,即由政府雇用的工人。
马里兰州的蒙特戈梅里县,离美国首都华盛顿半小时的路程,是许多高级文职人员的住宅区。在美国所有的县份当中,该县是家庭平均收入最高的。蒙特戈梅里县每四个就业人员中,就有一个是为联邦政府工作的。他们不担心失业,有同生活费用指数相联系的薪金。退休后,他们享有文职人员养老金,这种养老金也同生活费用指数相联系,并且不依赖于社会保险。许多人又极力取得领取社会保险金的资格,成了所谓拿双份养老金的人。
上述高级文职人员在蒙特戈梅里县的许多邻人,或许是大多数邻人,作为国会议员、院外活动人员、同政府订有合同的公司的董事长,也与联邦政府有某种联系。同华盛顿周围的其他住宅区一样,蒙特戈梅里县的发展是迅速的。最近几十年中,政府已变成了一种十分可靠而且发展很快的行业。
所有文职人员,甚至低级文职人员,都受到了政府的良好保护。根据大多数的研究报告,他们的平均薪金要高于同等私人企业雇员的薪金,并且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他们享有大量的额外优惠,而且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职业安全感。
正如《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所说:当(文职人员)管理规章激增,录满二十一大本,堆起来高达大约五英尺的时候,政府主管人员感到越来越难于解雇雇员了。与此同时,提级和增加工资则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几乎没有刺激、不受任何人控制的官僚统治机构。……
去年符合增加工资条件的一百万人当中,只有六百人的工资没有增加。几乎没有一个人被解雇;去年丢掉工作的联邦工作人员不到1%。
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事例:1975年1月,环境保护局一名打字员上班一贯迟到,以致他的上司要求将他解雇。这件事办了十九个月。如果把记录有关步骤的纸张连在一起,足有二十一英尺长。为了满足所有规章制度方面的要求,满足所有劳资协议上的要求,缺少哪一步骤也不行。
卷入这一过程中的有这个雇员的顶头上司、局长和副局长、人事处长、局内该部门的主管人、两名雇员关系专家、专门的调研办公室以及该办公室主任。不用说,这一大串官员为此而做工作是用纳税人的钱来支付的。
在州和地方政府各级,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在许多州以及象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大城市中,情况或者同联邦政府相类似,或者比联邦政府还要糟糕。纽约市落到它目前实际上的破产状态,主要是由于市政雇员工资的急剧增长,也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对提早退休人员给与优厚的养老金。在拥有大城市的各州,政府雇员的代表常常是州立法机关中的主要特殊利益集团。
没人提供保护
以下两种工人是得不到任何人保护的:一种是仅有一个可能的雇主的工人,另一种是没有任何可能的雇主的工人。
那些实际上只有一个可能的雇主的人,往往可以得到很高的报酬,因为他们的技能实在罕见,价值极高,只有一个雇主能够加以充分利用。
我们三十年代学习经济学时,教科书中的标准例子是棒球大王巴比·鲁思。他作为棒球之王译名叫做“最佳击球手”,他是那个时代最最受人欢迎的棒球选手。当时有两个主要的棒球俱乐部,不论鲁思为它们中的哪一个打球,都能使运动场卖满座。纽约扬基俱乐部恰巧拥有最大的运动场,因而它可以比任何其他俱乐部付给鲁思更多的钱。结果,扬基俱乐部实际上成了他唯一可能的雇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巴比·鲁思不能获得高薪金,但确实意味着没有人保护他;他不得不同扬基俱乐部讲价钱,把不为他们打球作为他进行威胁的唯一武器来使用。
没有可能选择雇主的人大都是政府措施的受害者。其中一类人我们已经提到过,即那些由于法定最低工资而找不到工作的人。正象前面已经指出的,他们中间许多人是政府措施的双重受害者:低劣的教育加上高额最低工资,后者阻碍了他们获得在职训练。
依靠政府救济的人多少处于相似的境地。只有当他们能挣到的收入足以补偿救济金或其他政府补助的时候,就业才对他们有利。但他们的劳务也许对于任何雇主都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七十二岁以下的依赖社会保险津贴生活的人,情况也是这样。如果他们可以挣得超过某一限额的收入,他们就会失掉其社会保险津贴。这就是近几十年超过六十五岁而仍然工作的人所占的百分比,为什么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对男性来说,这一比重由1950年的45%下降为1977年的20%。
其他的雇主
许多雇主的存在,可以为大多数工人提供最可靠而且最有效的保护。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只有一个可能的雇主的人,几乎或者根本得不到保护。保护工人的是那些愿意雇用工人的雇主。雇主对工人劳务的需求,使得他们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向工人支付其工作的全部价值。如果某一雇主不愿交付,另一雇主会支付。真正保护工人的,正是这种争夺工人劳务的竞争。
当然,其他雇主的竞争有时激烈,有时不激烈。一些机会会相互冲突,而另一些机会却不被人们所知。雇主要找到理想的受雇者,受雇者要找到理想的雇主,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们的世界并非尽善尽美的世界,因而竞争不能提供十全十美的保护。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工人说来,竞争是迄今被人们所发现或发明的最好的,也即害处最少的保护。
竞争的这种作用是我们一再提到的自由市场的一种特性。其他雇主的存在保护了工人免受其雇主的剥削,因为他可以到别处干活。其他工人的存在保护了雇主免受工人的剥削,因为他可以雇用别人。其他卖主的存在保护了消费者免受某一卖主的剥削,因为消费者可以到别的商店买东西。
我们的邮政服务质量为什么低劣?我们的长途火车服务质量为什么低劣?我们的中小学教育质量为什么低劣?都是一个原因造成的,就是我们实际上只能从一处得到上述服务。
结论
当工会用限制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办法来为其会员获取较高工资时,这种较高工资是通 过损害其他工人的利益获得的,这些工人发现他们的就业机会减少了。当政府向其雇员支付较高工资时,这种较高工资是通过损害纳税人的利益获得的。但是,当工人们通过自由市场获得较高工资和较好工作条件时,当工人的工资由于各厂商为得到最好的工人彼此进行竞争,由于工人们为得到最好的工作彼此进行竞争而增加时,这种较高工资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这种较高工资只能来自较高的生产率、较大的资本投资以及更加广泛推广的技能。整个馅饼是增大了——不仅工人得到的份额增大,而且雇主、投资者、消费者乃至税收官员得到的份额也增大了。
这就是自由市场制度在全体人民中间分配经济进步的果实的方式。这就是过去两个世纪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得到巨大改善的秘密所在。
本节内容概述
当工会用限制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办法来为其会员获取较高工资时,这种较高工资是通过损害其他工人的利益获得的,这些工人发现他们的就业机会减少了。当政府向其雇员支付较高工资时,这种较高工资是通过损害纳税人的利益获得的。但是,当工人们通过自由市场获得较高工资和较好工作条件时,当工人的工资由于各厂商为得到最好的工人彼此进行竞争,由于工人们为得到最好的工作彼此进行竞争而增加时,这种较高工资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这种较高工资只能来自较高的生产率、较大的资本投资以及更加广泛推广的技能。整个馅饼是增大了——不仅工人得到的份额增大,而且雇主、投资者、消费者乃至税收官员得到的份额也增大了。
这就是自由市场制度在全体人民中间分配经济进步的果实的方式。这就是过去两个世纪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得到巨大改善的秘密所在。
附录失业的成因和种类
技术性失业
技术性失业,是由于科技进步而引发的失业潮,例如工业革命引发的大量劳动人口的失业:蒸汽机、织布机、电灯等的发明;以及近代的自动化机械手臂、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各式自动化剪票口、未来的自动驾驶汽车等等。技术性失业通常产生卢德派之类的反科技进步组织,不过他们的抗争没办法对技术进步造成实质的阻碍。
由于近代的工业革命(目前是互连网、物联网科技以及自动化机械)可能造成绝大数人都遭到技术性失业,所以不少社会学家在研究新的制度与对策,以应付大范围技术性失业而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例如无条件基本收入就是一例。
摩擦性失业
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是指当人们放弃原来的职业再寻找新的工作,可能需要花费一段时间而出现的失业状况。因就业市场的资讯不流通,可能使得一些企业未能在短期内找到适合的劳工,而劳工也未能在这段时间找到工作,于是造成短期的失业现象。
现代社会中还有另一种摩擦性失业问题,拥有高学历的人士不一定能找到符合自己喜好的工作,也不愿意投身低阶劳动市场工作,造成不屈不就的窘境。此类失业属于自愿型失业,并非被裁员造成的非自愿型失业。这种失业往往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如隐蔽青年、双失中年(失业和失婚)、增加政府开支等。
结构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是指市场竞争的结果或者是生产技术改变而造成的失业,通常由于就业市场并不平衡,某些行业正扩张,另一些则衰退,造成部分工人失业。结构性失业通常较摩擦性失业持久,因为失业人员需要再训练或是迁移才能找到工作。
结构性失业的出现是因为经济结构、体制、增长方式等的变动,改变了工作技能的要求,导致失业的发生。由于失业工人并不具有合适的技能,因此,若失业工人并没有接受再培训或进一步的教育,他们便不能再获聘任,结构性失业问题因而会持续,影响长远的经济发展。
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被归类为自然失业,经济学家视这两种失业为正常现象。劳动人口中,属于该两种失业的劳动人口数目占劳动人口总数的百分比等于自然失业率。
自然失业率:失业率(%)=(摩擦性失业 + 结构性失业)÷ 劳动人口×100%
长期失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长期失业的定义是持续失业达12个月以上的劳工,长期失业数据值得关注的价值在于;这种劳工几乎就等于结构性失业者,此类劳工长期连续在社会上没有收入,很大概率已经耗尽储蓄,等于注定失去房屋和食物的获取能力成为社会问题最大的来源和社会暴动因素,也无法自费学习新技能来脱贫,更难进入职场等于生活在一种恶性循环中。若长期失业者没有得到官方的外力帮助几乎无法摆脱现状,因此长期失业数据对于政府施政有参考意义。
周期性失业
周期性失业(cyclical unemployment)是指由于经济中的总需求减少,导致劳动人口过剩,从而出现失业情况。这种失业被归类为非自愿性失业,因为人们是有能力并且愿意工作,只是社会的总需求减少以致劳动人口的数目未能与经济体系内的部门所提供的职位数目配合。由于总需求减少,伴随着的是经济周期改变,经济步入衰退期一直到低谷。如何解决周期性失业向来是经济学家的重点研究对象,经济学界里提出数种方法,例如:工人或工会自愿降低工资;增加对企业部门的投资诱导,提高总需求;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补充私人投资的不足,填补和总需求的差距等等。[4]
季节性失业
还有一种季节性失业(seasonal unemployment),相对以上三种失业情况来说,季节性失业并不足以对所有行业产生影响,也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失业”的类别或原因之一。它的涵义是社会中存在一些行业会在某些节日之前或者过后发生的失业情况。它常见于某些低技术工业,例如企业或工厂为了在重大节日前(例如圣诞节)尽快完成一个指定数量的产品,于是雇用不少额外工人以求尽快完成客户的订单,但在节日后进行裁员行动,将那些临时性工人解雇以减低长期成本。
古典式失业
古典式失业(classical unemployment),它跟季节性失业一样,并不是真正失业的原因,它是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对失业情况的解释。1890年,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马歇尔发表的经济学原理内,提出了局部均衡理论。这种理论以供给和需求的市场均衡来解释市场上的交易,供给主要由生产成本组成,需求则是由人们对该商品的边际效用组成。如果在单个生产单位的角度来说,劳动的工资也与劳动的边际产品有关,后者是生产单位多雇用一个人时,那个新雇用工人可以生产的产品,这边际产品决定全体工人的工资。英国经济学家,也就是所谓的“古典学派”认为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它的价格就是实质工资(等于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然价格)也由市场的均衡状况决定的。倘若人为推高了工资(例如法律订下的最低工资),供给量大于需求量造成超额,或者工资高于工人的边际产量,于是工人将被解雇,部分工人顺理成章失业。这解释提供解决方法,就是解雇工人是市场调节供给量的手段。因为这可以:
令人为的工资变成均衡价格,该行业的就业市场回到局部均衡。
对生产单位来说,边际产量势必因可变生产要素的减少而增加,边际成本减少,生产单位能够维持利润最大化。
古典式失业受人为的工资率和边际产量影响,所以是自愿性失业。
需求不足型失业(Demand-Deficient Unemployment)
人们可能已经拥有工作,但他们的生产力未必得到充分的利用,于是便会形成需求不足型失业(demand-deficient unemployment)及/或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就业不足总是永远存在于任何制度的社会。因为部分人们可能不愿意每日长时间工作;或者经济根本没有足够的全职工作去吸纳这些闲置的劳动力;即使实施计划经济的社会,政府也可能为了实现充分就业,而令到每单位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减少。就业不足率不包含于失业率内:
就业不足率(%) =(就业不足的人口 / 劳动人口)× 100%
第9章 通货膨胀的对策
先让我们比较一下两张差不多大小的长方形纸片。一张的背面大部分是绿颜色,正面有一幅林肯像,在这纸片的每一个角上印有数目字“五”,还有些别的图案。你用这纸片可以换到一定数量的食物、衣服或其他货物。人们将愿意和你做这种交易。
另外一张纸片也许是从一本印刷精美的杂志上剪下来的,正面可能也印有一幅画像、一些数目字和其他图案。背面可能也是绿颜色的。可是它却只适于点火。
不同在哪里呢?五美元的钞票上面印的东西解答不了这个问题。上面只是简单地印着“联邦储备券/美利坚合众国/五美元”,还有些小字:“本券为合法货币,可偿付一切公债和私债”。不多年以前,在“美利坚合众国”和“五美元”之间还有“可兑现”字样。看来这能说明两张纸片之间的区别。但它只是意味着,如果你到联邦储备银行要求出纳员兑现,他将给你五张同样的纸片,只是那数目字“五”换成了“一”,林肯的像换成了华盛顿的像。如果你从换得的五张纸片中拿出一张进一步要出纳员兑换,他会给你一些硬币。如果你把这些硬币熔化掉(尽管这样做是非法的),当作金属出售,肯定卖不到一美元,现在票子上印的字样虽然同样不说明问题,但至少是比较老实的。合法货币的含义是,政府将接受它作为向它偿债和纳税之用,法院将承认它们可以清偿按美元计算的债务。为什么私人进行货物和劳务的交易时也应该接受它们呢?
简单些回答,这是因为接受它们的每一个人都相信别人也会接受。这些绿色纸片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它们有价值。大家都认为它们有价值,是因为经验告诉大家它们有价值。要是没有一种大家共同接受的交易媒介(或这种媒介的数量不够多),美国就只能运用它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的一小部分;然而,大家共同接受的交易媒介的存在,却依赖于某种约定俗成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接受了一种从某种观点看来不过是虚构的东西。
但不论是约定俗成还是虚构,都不是脆弱的东西。相反,拥有一种共同的货币是非常有用的,以至人们即使在信念受到极严重的挑战时也仍然死抱住这种虚构不放。我们将要看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货币发行者得以从通货膨胀中得到好处,从而诱使他们造成通货膨胀。但也不是说这种虚构是不可摧毁的:“不值一文”(not worth a Continental)这个短语,使人想起美国大陆会议为了支持美国革命而过量发行的大陆货币的虚构是怎样被摧毁的。
虽然货币的价值是虚构的,但货币却具有非常有用的经济职能。不过这也只是一层面纱。决定一个国家财富的“真正的”力量,是它的公民的能力、他们的勤劳和智慧、他们所能利用的资源以及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方式等等。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一百多年以前写道的,“简言之,在社会经济中,没有什么东西从本质上来说比货币更不足道的了;它仅仅是一种发明物,用来节省时间和劳动。它是一种机器,用来把事情办得便捷,没有它,同样能办事,只是不那么便捷罢了。而且它同其他许多机器一样,一旦出了毛病,就只发挥它特有的、独立的作用。”
这样描述货币的作用完全正确,只是我们得承认,社会拥有的发明物,哪一件出毛病时也没有货币造成的危害大。
我们已经讨论过一个例子:大萧条,那时由于急剧减少货币供应量,货币出了毛病。本章讨论的是相反的、更常发生的情况:由于急剧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出了毛病。
货币种种
历史上,曾有许多东西被当作货币。“金钱”(pecuniary)这个词,来自拉丁文中的“pecus”,意为“牛”。牛是许多曾充当货币的东西之一。其他还有盐、丝、毛皮、鱼干儿以至羽毛,在太平洋的雅浦岛上,人们曾用石头当货币。贝壳和珠子是用得最广的原始货币。在纸片和会计用的笔取得胜利以前,在比较先进的经济中,金属——金、银、铜、铁、锡——曾经是使用最广泛的货币。
所有这些曾用来充当货币的东西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在特定的地方和时间,人们接受它来交换货物和劳务,相信别人也同样会接受。
美洲早期的定居者用来同印第安人作交易的“瓦姆庞普”(wampum)就是一种贝壳,与非洲和亚洲使用的贝壳相类似。美洲殖民地使用过的一种最有意思、最富有启发意义的货币,是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使用的烟草货币:“1619年7月31日〔约翰·史密斯上尉登上美洲,在詹姆斯敦建立起在新世界的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之后十二年〕,弗吉尼亚州第一届议会通过的第一个法律就是关于烟草的,它规定‘上等烟草的价格为三先令一磅,次等烟草的价格为十八便士一磅。’……烟草成了当地的货币。”
烟叶在各个时期都被宣布为唯一合法的货币。直到美国革命以后很久,将近两个世纪的一段时期,烟草一直是弗吉尼亚州及其邻近殖民地的主要货币。殖民者就用它来购买食物、衣着,用它来纳税——甚至用它来买新娘子:“弗吉尼亚州的作家威姆斯牧师说,每当有船从伦敦到达的时候,去看看漂亮的弗吉尼亚小伙子们个个挟着一捆上好的烟草跑到岸边,每人带回一个美丽而贤惠的年轻妻子,是令人开心的事。”另一位作家引用了这段话之后说,“他们一定既漂亮又高大,才能挟着一捆一百到一百五十磅重的烟草飞跑。”
当时烟草和货币同时流通。它最初按英国货币规定的价格高于种植它的成本,于是种植者就一心一意的种,产量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应量不仅表面上有所增加,而且实际上确实增加了。与通常的情况一样,由于货币供应量比可以买到的货物和劳务的数量增加得快,因而发生了通货膨胀,按烟草计算的其他东西的价格急剧上涨。大约半个世纪之后这场通货膨胀结束时,按烟草计算的物价上涨了四十倍。
烟草种植者对这场通货膨胀极为不满。按烟草计算的其他东西的价格如果上涨,烟草能够购买的货物量就会减少。按货物计算的货币的价格,是按货币计算的货物价格的倒数。自然,烟草种植者要求政府提供帮助。于是通过了一项又一项法律,禁止某些人种植烟草;要求毁掉一部分已收获的烟草;禁止种植烟草一年。但这些都无济于事。最后,人们自己行动起来,结成一帮一伙,跑到乡下去毁坏地里的烟草:“破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议会在1684年4月通过了一项法律,宣布这些破坏分子的行动极其严重地扰乱了社会治安,他们的目的是颠覆政府。同时宣布,如果有八个以上的人纠合在一起毁坏烟草田,就要判他们叛国罪,处以死刑。”
烟草货币生动地说明了一条最古老的经济学法则,即格雷欣法则:“劣币逐良币。”烟草种植者在纳税或者支付其他按烟草计算的债务时,自然用质量最差的烟草,而保留质量最好的供出口,以换回“硬”货币,即英镑。结果作为货币而流通的往往是质量低劣的烟草。人们挖空心思把烟草弄得样子好一点:“马里兰州在1698年发现有必要通过法律来防止人们弄虚作假,人们经常在大桶的上面盖一层好烟叶,而下面塞的却是甘蔗叶。弗吉尼亚州在1705年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但显然并没有解决问题。”
“1727年烟票合法化后,”质量问题才有所缓和。“所谓烟票在性质上同存款单相类似,由验收人员签发。法律规定它可以在签发烟票的库房所在地区流通,并可以用它偿还一切债务。”尽管实行烟票制的弊病很多,“但直到十九世纪前夜,这种收据却起到了通货的职能。”
这并不是最后一次把烟草当作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和日本的集中营里,人们曾广泛地拿纸烟作为交易的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领军当局对德国的法定货币规定了远远低于收盘水平的最高限价。结果使德国的法定货币丧失了作用。人们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作交易,小交易用纸烟作媒介,大交易用法国白兰地酒作媒介——无疑,这两种东西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为流通的货币。路德维希·艾哈德的货币改革结束了这一富有启发意义的——而又具有破坏性的——插曲。
弗吉尼亚烟草货币所表明的一般原则,在当代仍然适用,虽然政府发行的纸币和叫做存款的簿记项目,取代商品和库房的进货收据,成了社会的主要货币。
现在仍然同当初一样,如果货币数量增加的速度,超过能够买到的货物和劳务数量增加的速度,就会发生通货膨胀,按这种货币计算的物价就会上涨。这同货币量为什么增加不相干。在弗吉尼亚州,烟草货币量增加,产生了按烟草计算的物价的上涨,是因为用劳动和其他资源生产烟草的成本急剧降低了。在中世纪的欧洲,金银是主要的货币,按金银计算的物价上涨,是因为西班牙从墨西哥和南美洲弄来的贵金属充斥欧洲市场。十九世纪中叶,世界范围按黄金计算的物价上涨,是因为人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后来,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1914年,物价上涨是因为成功地在商业上应用了氰化处理法,人们可以用这种方法从低品位矿石——主要是在南非——中提取黄金。
今天,大家接受的交易媒介,不同任何商品发生关系,在各大国,货币量由政府决定。政府,也只有政府,应对货币量的迅速增加负责。这个事实是造成人们目前对于通货膨胀的原因和治法众说纷坛的主要缘故。
造成通货膨胀的近因
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一种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疾病,如不及时制止会摧毁整个社会。
例子是很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和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有时一夜之间上涨一倍或一倍以上——在一个国家里为共产主义奠定了基础,在另一个国家里为纳粹主义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便利了毛泽东击败蒋介石。在巴西,通货膨胀率在1954年达到大约100%,由此产生了军人政府。比这严重得多的通货膨胀导致了1973年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倒台和1976年阿根廷庇隆政府的倒台,两国都由军政府接管了政权。
没有一个政府愿意承担制造通货膨胀的责任,哪怕是不那么恶性的通货膨胀。政府官员总是能够为通货膨胀找出种种理由——贪得无厌的企业家、得寸进尺的工会、挥霍浪费的消费者、阿拉伯的酋长、恶劣的气候、或者别的什么更不着边的理由。不错,企业家贪得无厌,工会得寸进尺,消费者挥霍浪费,阿拉伯酋长们提高了石油价格,气候经常不好。所有这些可以使个别商品的价格上涨;但它们不会造成物价的普遍上涨。它们可以造成通货膨胀率的一时涨落。但它们不会造成持续的通货膨胀,理由很简单:这些被指控的罪犯没有哪一个拥有印刷机,能印出那些装在我们口袋里的纸片,也没有哪一个可以合法地授权会计在帐册上记入与那些纸片相等的项目。
通货膨胀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现象。南斯拉夫,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其通货膨胀率在欧洲国家当中可以说属于最高之列;瑞士,一个资本主义的堡垒,其通货膨胀率则属于最低之列。通货膨胀也不是共产主义的现象。中国在毛泽东统治下几乎没有通货膨胀;意大利、英国、日本和美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十年里则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当今世界上,通货膨胀是印刷机带来的现象。
承认严重的通货膨胀无论在哪里都总是一种货币现象,这还只是理解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治法的开始。更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的政府过于急速地增加货币的数量,为什么它们明知有潜在的危害,还是要制造通货膨胀?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值得再稍稍谈一下上面那个命题,即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尽管这个命题意义非常重大,尽管大量历史事实证明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它却仍然广泛地遭到否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散布烟幕,试图掩盖它们制造通货膨胀的责任。
如果能买到的货物和劳务的数量——简言之就是产量——能够同货币的数量以同样快的速度增加,那么,物价会趋于稳定。物价甚至可能逐步下降,因为人们收入增多后,将希望以货币的形式保存更多的财产。通货膨胀发生在货币的数量明显地增加,而且增加速度超过产量的增加时,每一单位产量的货币量增加得越快,通货膨胀也越剧烈。在经济学里,也许没有哪个命题比这个命题更为正确的了。
产量受到可利用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限制,也受到知识水平和运用知识的能力的限制。产量至多只能相当缓慢地增加。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的产量每年平均增加约3%。即使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年代,每年产量的增长也只是在10%左右。商品货币的数量也受到同样的物质上的限制,不过正如烟草、新世界的贵金属和十九世纪的黄金等例子所表明的,商品货币的增长速度有时比一般产量的增长速度快得多。现代货币——即纸币和簿记项目——是不受物质限制的。货币数量,也就是美元、英镑、马克或其他货币单位的数量,可以以任何速度增长,而实际上它们的增长速度有时高得惊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流通货币平均每月增加300%以上,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多,物价也以同样的速度上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流通货币每月平均增加12,000%以上,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物价甚至涨得更多,每个月上涨近20,000%。
1969至1979年美国发生轻得多的通货膨胀时,货币的数量平均每年增加9%,物价每年上涨7%。这十年产量的平均增长率为2.8%,这一比率大体上是上面两个百分比之间的差额。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货币数量的增长一般远远超过产量的增长;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讲到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时,没有附加任何有关产量的条件。这些例子还告诉我们,货币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并不是完全相等的。但是,就我们所知,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例子:一场严重而持久的通货膨胀,不伴随着大致相等的货币增长速度;也没有这样的例子,货币数量的急速增加,不伴随着大致相等的通货膨胀率。
几张图表(图1-5)表明,近年来这种关系始终如此。图中的实线是有关国家每单位产量的货币数量,记录的是从1964年到1977年每年的情况。另一条线是消费品价格指数。为了便于比较,两条线都用平均值在整个时期中所占的百分比来表示(两条线都以1964-1977为100)。两条线必然具有相同的平均水平,但如果数字计算精确的话,两条线并不一定在任何一年都一样。
图1美国的两条线几乎重合在一起。正如另外几张图表所表明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美国所独有的。虽然别国两条线之间的距离比美国的要大,但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两条线都非常相象。不同的国家有很不相同的货币增长率。但无论是哪个国家,这种不同总有与之相称的不同的通货膨胀率。巴西是个最极端的例子(图5)。它的货币增长率高于任何其他国家,因而其通货膨胀率也高于其他国家。
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货币量的迅速增加是因为物价迅速增加,还是相反?一条线索是,在大部分图表上,表示某年货币量的点总要比那一年物价的相应指数早六个月。考察一下决定这些国家货币量的制度因素和大量历史事件,可以得到更为明确的证据。在这些事件中,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是十分清楚的。
一个极好的例子是南北战争。南方主要是靠印刷机来资助战争,在这一过程中,从1861年10月到1864年3月,通货膨胀率平均每月为10%。为了制止通货膨胀,联邦实施了货币改革:“1864年5月,货币改革生效,货币量减少了。一般物价指数显著下降……尽管当时联邦军队侵入,军事上濒于失败,对外贸易减少,政府陷于混乱,联邦军队的土气低落。减少货币量对物价产生的明显影响,超过了这些强大的力量。”
这些图表排除了许多被广泛接受的关于通货膨胀的解释。工会是方便的替罪羊。它们被指责运用垄断力量强求提高工资,这使成本增加,物价上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日本和巴西的图表所表现的关系同英国、德国以及美国的一样呢?在日本,工会的力量微不足道;在巴西,工会只有得到政府的默许才能存在,而且要受严密的控制;而在英国,工会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会都强大;在德国和美国,工会的力量也很强大。工会可以为其会员提供有用的服务,也可以通过限制别人的就业机会造成许多损害,但是它们不制造通货膨胀。工资的增加超过生产率的增加,这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
同样,企业家也不造成通货膨胀。他们提高标价,是其他力量的结果或反映。通货膨胀严重的国家的企业家,肯定不会比通货膨胀轻微的国家的企业家更为贪婪,一个时期的企业家也不会比另一个时期的企业家更为贪婪。那为什么通货膨胀在某些地方、某些时期比在别的地方、别的时期厉害得多呢?
另外一个常见的解释,特别是企图推卸责任的政府官员经常给予的解释,是说通货膨胀是从国外输入的。这个解释,当大国的通货通过金本位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是正确的。在那时,通货膨胀是一种国际现象,因为许多国家都用同一种商品作为货币,只要什么使得这种商品货币的数量较快地增加,就会影响到它们全体。但就近年来说,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它是正确的话,为什么不同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这样不同?七十年代初期,日本和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每年达30%以上,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10%左右,德国的不到5%。我们可以说通货膨胀是世界范围的现象,因为它同时发生在许多国家里——正如高额政府开支和巨额政府赤字是世界范围的现象一样。但通货膨胀并不是一种国际现象,因为每个国家能单独控制自己的通货膨胀……正如高额政府开支和巨额政府赤字不是由每个国家控制力以外的力量造成的一样。
关于通货膨胀的另一种常见的解释是生产率低下。但让我们来看一下巴西的情况。该国产量的增长率在世界上属于最高之列,而其通货膨胀率也属于最高之列。确实,影响通货膨胀的是每一单位产量的货币量,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实际上,产量的变化赶不上货币量的变化。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经济福利来说,没有什么比提高生产率更为重要的了。如果生产率每年增长3.5%,二十年后,产量就能增长一倍;如果每年增长5%,十四年后就可以增长一倍——差别甚大。但是,生产率对通货膨胀只起极微小的作用,货币才起主要作用。
阿拉伯酋长们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呢?它们给我们强加了沉重的负担。石油价格陡涨,减少了我们所能得到的货物和劳务,因为我们得出口更多的货物和劳务支付石油。产量的减少提高了价格水平。但那影响也就这一下子。价格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对通货膨胀率造成持久的影响。在1973年那次石油危机之后五年里,德国和日本的通货膨胀减慢了,德国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从大约7%减到不足5%,日本从30%以上减到5%。在美国通货膨胀在那次石油危机之后一年达到最高峰,约为12%,1976年降到5%,然后在1979年又升到13%以上。这些大不相同的经历,能用所有国家共同遭受的一次石油危机来解释吗?德国和日本是100%依靠进口石油的,可是它们在降低通货膨胀率方面,却比只有50%的石油依靠进口的美国、或是已经成为一个大石油生产国的英国做得好。
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基本命题上来。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货币量比产量增加得更快造成的。货币量的作用为主,产量的作用为辅。许多现象可以使通货膨胀率发生暂时的波动,但只有当它们影响到货币增长率时,才产生持久的影响。
货币为什么过度增加?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这个命题虽然重要,但它只是解答通货膨胀的原因和治法的开始。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指导我们找出根本的原因并限制可能的治法。但它只是解答的开始,因为更深一层的问题是货币为什么会过度增加。
不论烟草货币或是以金银为本位的货币是什么情况,就今天的纸币来说,货币的过度增加,从而通货膨胀,是政府制造的。
在美国,过去十五年左右货币加速增加,有以下三个相关的原因:第一,政府开支迅速增加;第二,政府的充分就业政策;第三,联邦储备系统执行的错误政策。
政府如果用征税或向公众借款的办法来增加开支,那将不会招致货币增长率加快,因而也就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支增多,而公众开支减少。政府开支的增加,被私人消费开支和投资开支的减少抵消了。但是,通过征税和向公众借款来增加政府开支,在政治上是不高明的做法。我们许多人欢迎政府增加开支,却很少有人欢迎增加捐税。政府向公众借款,会提高利率,从而减少私人对资金的利用,个人为购买新住宅获得抵押贷款以及企业借款都要付较高的利息,遇到较大的困难。
除此而外,政府增加开支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货币数量。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提到的,要做到这一点,美国政府可以让美国财政部——政府的一个部门——卖公债给联邦储备系统——政府的另一个部门。联邦储备系统用新印刷的联邦储备券或是为财政部记入一笔存款,来支付公债。财政部于是可以用这些现钱或是可以向联邦储备系统取现钱的支票来偿付账款。当这些新增的高功率的货币被它最初的接收者存入商业银行时,它就成了商业银行的储备,以此可以更大规模地增加货币量。
用增加货币量的办法资助政府开支,对于总统和国会议员都常常是最富有吸引力的。这使他们能够增加政府开支,给选民一些甜头,而无需征税来为此付出代价,也无需向公众借款。
美国近年来货币增加较快的第二个原因,是试图实现充分就业。这个目标,对于数目众多的政府计划来说,是值得称道的,但其结果却令人很不满意。“充分就业”这个概念的含义,比表面看来要复杂含糊得多。在一个生气勃勃的世界上,新产品层出不穷,旧产品不断被淘汰,需求从一种产品转向另一种产品,发明创造时常改变生产方法,总之,一切都在运动,因而,劳动力也应经常流动。人们从一种工作转做另一种工作,其间常空闲一段时间。有些人脱离他们所不喜欢的工作,却还没有找到另外的工作。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需要花费一段时间寻找工作,也需要一些时间体验各种不同的工作。此外,对劳动力市场的自由运行的阻碍——工会的限制、最低工资,等等——增加了工人找到合适工作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平均多少人就业算是充分就业呢?
在政府开支和政府税收方面,也有不对称的问题。凡认为有助于增加就业的措施,在政治上都是吸引人的。凡认为会增加失业的措施,在政治上都是不吸引人的。结果是造成政府政策上的一种偏向,政府总是试图实现不切实际的充分就业目标。
这与通货膨胀有双重关系。首先,人们认为政府开支有助于增加就业,政府税收会减少私人开支,从而增加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就业政策往往使政府增加开支、降低税收,用增加货币量的办法而不是用征税或向公众借款的办法来弥补由此产生的赤字。其次,联邦储备系统不用资助政府开支的办法也能增加货币量。它可以用新制造的高功率的货币买进已发行的政府公债,从而增加货币量。这使银行能够发放更大量的私人贷款,因而人们认为联邦储备系统买进政府公债有助于增加就业。在人们要求实现充分就业的压力下,联邦储备系统的政策同政府的财政政策一样具有造成通货膨胀的倾向。
这些政策并没有实现充分就业,而是带来了通货膨胀。正如詹姆斯·卡拉汉首相在1976年9月对英国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一篇有勇气的讲话中所说的:“我们过去常常认为,只要大手大脚地花钱就可以渡过衰退时期,可以用削减税收和增加政府开支的办法增加就业。现在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你们,这种抉择已不复存在;如果说它存在过而且起过作用,那也只是靠了给经济注射更大剂量的通货膨胀,而下一步接着就是更高水平的失业。这就是过去二十年的历史。”
美国近年来货币量大增的第三个原因,是联邦储备系统执行了的错误政策。联邦储备系统的政策在人们要求实现充分就业的压力下不但具有通货膨胀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由于该系统试图追求两个互不相容的目标而变得更为严重。联邦储备系统有权控制货币量,它在口头上赞成这个目标。但象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狄米特律斯(他躲开爱着他的海丽挪,而追求爱着另一个人的赫米亚)一样,联邦储备系统不是把心用在控制货币量上,而是用在控制它无权过问的利率上。结果在两条战线都遭到了失败:货币量和利率都大幅度波动。这种波动同样具有造成通货膨胀的倾向。联邦储备系统牢记1929年到1933年犯的灾难性的错误,在货币增长率向下波动时急忙加以纠正,而货币增长率向上波动时则反应非常迟钝。
政府开支增长、充分就业政策和联邦储备系统着迷于利率的后果,就象处在上坡道上的滑行车一样。通货膨胀率升升降降,每次上升都使通货膨胀达到一个较前次顶峰更高的水平,每一次下降都使通货膨胀保持高于前一次的低点。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政府税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增加,只是不象开支增加得那样快,在这种情况下,赤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增加。
这种情况并不是只发生在美国,也不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事。从远古以来,当权者——无论是国王、皇帝或议会——都想用增加货币量的办法来获取资源进行战争,建立不朽功业或达到其他目的。他们常常受到这种诱惑。每当他们真的这样做的时候,紧跟着就会发生通货膨胀。
近两千年以前,罗马皇帝戴奥克莱迁曾用“降低铸币成色’的办法使通货膨胀——用貌似银币的合金币代替银币,其中银的成分越来越少,不值钱的合金成分越来越多,直到只是“贱金属表面镀一层银子而已。”现代政府采用的方法是印纸币和入账——但那古老的方法并没有完全消失。一度曾经是足色的美国银币,现在变成了铜币,镀的一层甚至不是银而是镍。而且,一种小号的苏珊·B.安东尼铸币取代了一度是足色的银元。
政府从通货膨胀中得到的收入
用增加货币量的办法资助政府开支,看起来象在变魔术,能凭空变出东西来。举个简单的例子,政府建造一条道路,筑路费用新印的联邦储备券支付。看起来好象大家都得到了好处,筑路工人得到工资,可以用来买吃的、穿的、住的。没有谁缴更多的税。却在原来没有路的地方有了路。是谁付的钱呢?
回答是所有持有货币的人为这条路付了钱。新增加的货币因为被用来招收工人筑路而不是雇用工人从事其他生产性活动,因而物价上涨。新增加的货币进入流通过程,从筑路工人手里转到他们向之买货的卖主手里,从这些卖主又转给别的卖主,等等,从而物价的上涨得到了维持。物价上涨意味着,人们原先持有的钱现在只能买到比原先少的东西。为了在手头积存足够的钱,能够购买从前那样多的东西,他们将不得不节省开支,把一部分收入用来抵补这个差额。
增印纸币无异于对人们持有的货币征税。如果新增加的货币使物价上涨1%,那么,每一个持有货币的人实际上缴纳了一笔税款,数额相当于他持有的货币总数的1%。他现在必须持有额外的纸片(或存款)以得到同从前一样的购买力。这些额外的纸片同他口袋里或保险箱里(或入了账的)的其他纸片税款的收据。
同上述税款相对应的实物,是使用筑路所耗费的资源本来可以生产的货物和劳务。那些为维持原有货币的购买力而节省开支的人,放弃了这些货物和劳务,使政府能够把这些资源用于筑路。
由此,你可以理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讨论通货膨胀问题时,为什么会写出下面这样一段话:“摧毁现存社会基础的最狡猾而又最可靠的方法,莫过于发放通货。这一过程把经济规律的全部看不见的力量都投到破坏的方面,而这样做时使用的方法,一百万人中间也不会有一个人能够弄得清楚。”
新增印的货币和记入联邦储备银行账册的额外的存款,只相当于政府从通货膨胀中得到的收入的一部分。通货膨胀还自动提高实际税率,从而间接地增加政府收入。当人们的货币收入随着通货膨胀而增加时。收入便被推上较高的一档,税率也就提高。公司收入因为没有扣除足够的折旧费和其他成本也人为地膨胀。一般说来,如果通货膨胀率为10%而收入也增加10%的话,联邦的税收会增加15%以上——这样,纳税人要赶上趟就不得不越跑越快。这个过程使总统、国会、州长和议员们能够装作减税的样子,而他们真正做的不过是不让赋税一次增加得过多而已。每年都说要“减税”,然而从来没有减少过。相反,如果正确计算一下的话,赋税实际上增加了:在联邦政府一级,税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1964年的22%增加到1978年的25%;在州和地方政府一级,从1964年的10%增加到1978年的15%。
通货膨胀给政府带来收入的第三种方法,是为政府偿还——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叫做拒付——部分公债。政府借入的是美元,偿还的也是美元。但由于通货膨胀,它偿还的美元能买的东西要比它借入的美元能买的东西少。如果在这期间政府为债务支付的利息足以抵补债权人因通货膨胀受到的损失,那政府并不能因通货膨胀得到纯收益。但是就大部分公债来说,并非如此。储蓄券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假定你在1968年12月购进一张储蓄券,保留到1978年12月兑现。你在1968年花三十七点五美元购买为期十年的、面值为五十美元的储蓄券,到1978年兑现时你可得到六十四点七四美元(因为在这期间政府提高了利率以在某种程度上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但实际上到1978年,你要花七十美元才能买到1968年花三十七点五美元可以买到的东西。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不仅你取回的只有六十四点七四美元,而且你还得为你得到的和付出的之间二十七点二四美元的差额缴纳所得税。结果是你为有幸借钱给政府付出了代价。
靠通货膨胀来还债意味着,尽管政府年复一年有大量赤字,它的美元债务越来越多,但这债务就购买力来说远没有增加那么多,而且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还下降了。从1968年到1978年这十年间,联邦政府累计赤字超过二千六百亿美元,但负债额在1968年占国民收入的30%,1978年只占28%。
通货膨胀的医治
医治通货膨胀,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因为货币量的过度增加是通货膨胀的唯一重要原因,因而降低货币增长率是医治通货膨胀的唯一方法。问题不在于知道该做什么。这是很容易的。政府必须降低增加货币量的速度。问题是要有政治上的决心来采取必要的措施。通货膨胀这一疾病一旦到了晚期,医治它就得花很长时间,而且会有痛苦的副作用。
可以举两个医学上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例子是:一个青年得了布尔吉尔氏病,这种病将阻断血液供应,会导致坏疽。这个青年人将失去他的手指和脚趾。治法说来简单:就是戒烟。那青年人缺乏这样做的意志,他的烟瘾太大了。他的病在一种意义上是可以医治的,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无法医治。
另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酗酒。当酒鬼开始喝酒的时候,先是感到非常痛快,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则会感到头痛恶心,忍不住喝“解醉酒”来减轻痛苦。
通货膨胀的情况也是这样。当一个国家开始发生通货膨胀的时候,初始的效果似乎很好。增加的货币量使得任何因此而得到更多货币的人——当今主要是政府——可以多花一些钱,而无需任何别人少花钱。就业机会增多,生意兴隆,几乎可以说是皆大欢喜,这是最初的情况,也是好的效果。但随后,开支的增大使物价上涨;工人们发现他们的工资虽然按美元计算有所提高,可能够买到的东西却减少了;企业家发现他们的成本上升,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他们能够更快地提高价格,否则销售额的增加并不会带来他们所预期的利润。不良效果开始出现:物价上涨,需求缺乏弹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同时发生。和那个酒鬼一样,人们这时想的是更快地增加货币量,这就使我们坐上了前面提到的那种滑行车。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加大数量——酒或是货币——来给那酒鬼或是经济一个同样的“刺激”。
酗酒和通货膨胀相类似,医治的方法也相同。治酗酒的办法是干脆宣布:停止饮酒。这难以办到,因为这一回是不良效果在前,而好的效果在后。刚戒酒的人感到很难受,然后才能到达乐土,不再是几乎不可抗拒地想再喝一杯。通货膨胀也是这样。放慢货币增长率,在开始的时候会带来痛苦的副作用: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暂时偏高,通货膨胀率暂时并不降低多少。好处要在一两年后才出现:通货膨胀率降低,经济比较健康,有了非通货膨胀性迅速增长的潜势。
痛苦的副作用,是酒鬼或通货膨胀的国家难以戒除的一个原因。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至少在病的早期比第一个原因更为重要:即缺乏真正的戒除的愿望。饮酒者津津有味地品酒;不愿承认自己是酒鬼;也不认为应该去治疗。通货膨胀的国家处于同样的情况。它往往认为通货膨胀是暂时的现象,没有什么了不起,是异常的外部情况造成的,它会自行消失——可实际上通货膨胀从来没有自行消失过。
而且,我们许多人也喜爱通货膨胀。我们自然喜欢看到我们买的东西降价,或至少价格停止上涨。但是我们更喜欢看到我们卖的东西涨价——不论是我们生产的货物,我们的劳务,还是我们拥有的房屋或其他东西。农民抱怨通货膨胀,却聚集到华盛顿要求提高他们的产品的价格。我们其他人大都也这样或那样地做着同样的事情。
通货膨胀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原因之一,是别人吃苦头的时候有些人却得到很多好处;社会划分成胜者和败者。胜者认为他们碰到的好事,是他们自己的远见、谋虑和主动的自然结果。他们认为那些坏事,例如他们买的东西涨价,是他们所控制不了的外部力量造成的。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会说他反对通货膨胀;他的通常的意思是他反对他所碰到的坏事。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几乎每一个拥有房产的人在过去二十年间都因通货膨胀得到了好处,因为他的房子的价值急剧增高。如果房子是靠抵押贷款购买的,那利率通常低于通货膨胀率。结果,付了叫做“利息”和叫做“本金”的钱,就实际偿清了贷款。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定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是一年7%。如果你借入了一笔一万美元的抵押贷款,只付利息,那么一年之后,这笔贷款的购买力只相当于一年前的九千三百美元。实际上你就少欠了七百美元——正好是你付的利息的数目。实际算来,你使用这一万美元没有付任何东西。(由于在计算你的所得税时要除去这笔利息,你实际上还有所得。你借了钱还得到报酬。)对于房产拥有人来说,这种效果是明显的,因为他的房屋的价值迅速上涨。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为储蓄信贷协会、互济银行或其他机构提供资金,使它们能够发放抵押贷款的小储户来说,却是损失。这些小储户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政府严格限制这些机构付给其储户的最高利率——据说是为了保护储户。
因为高额政府开支是造成货币过度增长的一个原因,所以减少政府开支是有助于减少货币增长的一个因素。在这里,我们也倾向于患精神分裂症。我们都喜欢看到政府开支下降,只要不是对我们有利的开支;我们都喜欢看到赤字减少,只要是靠征别人的税来减少赤字。
但是,通货膨胀的加速发展,迟早会对社会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带来大量的不公平和苦痛,以至真正的公众意志会发展起来,对通货膨胀采取措施。通货膨胀发展到什么程度才会发生这种情况,要看有关的国家和它的历史。在德国,通货膨胀程度不高就会发生,因为德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过可怕的经验;在英国和日本,发生这种情形时的通货膨胀水平要高得多;而在美国还不曾发生。
医治的副作用
我们再三读到,较高的失业率和缓慢的增长是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我们必须面对的选择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或者较高的失业率;政府当局已安于或正在积极地促进较慢的增长和较高的失业率,以医治通货膨胀。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虽然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放慢了,平均失业水平也上升了,但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却越来越高。我们既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又有较高的失业率,二者兼而有之。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经验。这是怎么回事呢?
回答是,缓慢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失业率并不是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而是医治奏效时产生的副作用。许多政策在妨碍经济增长和增加失业的同时,又增加通货膨胀率。这就是我们采取的一些政策的情况——零星的物价和工资管制,政府对企业干预的增多,都伴随以政府愈来愈大的开支和货币量的急速增加。
另一个医学上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治法和副作用的区别。你患了急性阑尾炎,医生建议做阑尾手术,而且告诉你手术之后要卧床休息一段时间。你拒绝动手术,而是在床上躺那么一段时间,把这作为痛苦较少的治疗方法。人们也许感到这非常荒唐可笑,但这在各方面都同在失业问题上混淆副作用和治疗方法一样。
医治通货膨胀,副作用是痛苦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懂得为什么产生副作用,并设法减轻它们,产生副作用的根本原因,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说明了。那就是变化的货币增长率,对由物价制度传递的情报产生干扰,因而使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作出不适当的反应,而这需要时间来加以克服。
首先,考虑一下当货币开始膨胀性增长时会发生什么情况。用新创造的货币偿付的较高的开支,对于出售货物、劳动或其他劳务的人来说,同别的开支并无不同。例如,卖铅笔的人发现他能够按原先的价格售出更多的铅笔。他开始时就是这样做而没有改变铅笔的价格。他向批发商定购更多铅笔,批发商又向制造商订货,制造商又向原料供应商定货,等等。如果铅笔需求的增加是以其他某种东西的需求减少为代价,譬如说圆珠笔,而不是货币膨胀性增长的结果,则铅笔这方面订货的增加,会伴随着圆珠笔这方面订货的减少。铅笔,随后是用来制造铅笔的原料,会涨价;圆珠笔和制造圆珠笔的原料会跌价;但物价的平均水平并没有理由发生变化。
当对铅笔的需求增加是起因于新创造的货币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时,对铅笔、圆珠笔以及其他大部分东西的需求会同时增加。总的(货币)支出增多了。但是铅笔的销售者并不知道这一点。他还是象往常那样,开始的时候保持他平常的售价,愿意多卖一些铅笔,直到他认为他能够重新进货的时候。但是现在铅笔这个方面订货的增加,是同圆珠笔以及其他许多货物订货的增加一起发生的。由于订货的增加导致了对劳动和原料的需求相应增加,因而工人和原料生产者最初的反应会同零售商一样——加班加点增加生产,并且也提高价格,他们认为社会对他们提供的东西的需求增加了。但是这一次没有任何抵消物,没有大体上同增加的需求相当的减少的需求,没有同上涨的价格相当的下跌的价格。自然,这一点在开始时是不明显的。在一个富有活力的世界上,需求总是在变化,某些物价上涨,某些物价下跌。总的需求增加的信号往往同反映相对需求变化的特定信号混在一起。正因为这个原因,货币增长率加快的副作用看起来象是经济繁荣和就业人数增多。但迟早总的需求增加的信号会到达。
这一信号一旦到达,工人、制造商和零售商就会发现他们受骗了。他们对他们销售的那一点东西需求的增加作出反应时,误以为这需求增加是专对他们的,因此不会对他们购买的许多东西的价格产生很大影响。当他们发现自己错了时,他们就进一步提高工资和价格——不仅对需求的增加作出反应,而且把他们购买的东西的价格上涨也计算在内。我们于是就陷于物价和工资螺旋上升的过程中,这本身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货币的增加不进一步加速,对就业人数和产量的最初刺激就会转向反面;就业人数和产量都会因工资和物价的上涨而趋于下降。最初的一阵兴奋之后,就是醉醒后的不适。
发生这些反应需要时间。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在美国、英国和一些其他西方国家,大致平均要六到九个月,货币的增加才完成其经济过程,使经济和就业人数增长。再要十二到十八个月的时间,货币的增长才明显影响到物价水平,产生或加速通货膨胀。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所需要的时间之所以很长,是因为除战时外,这些国家的货币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的批发价格平均同二百年前差不多,美国的同一百年前差不多。在这些国家,通货膨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因而是一种新现象。通货膨胀率时高时低,没有一定的长期趋势。
许多南美洲国家没有那么幸运的遗产。在这些国家,货币增长对经济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要短得多——至多几个月。如果美国不纠正近来通货膨胀率大幅度变化的倾向,产生经济影响所需要的时间在美国也将会缩短。
放慢货币增长率后出现的情况,同上面说的情况一样,只是方向相反。开支的最初减少会被认为是对某些特定产品的需求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后,这将导致产量和就业人数的减少。再过一段时间,通货膨胀减缓,伴之以就业人数增加和产量提高。酒鬼经过一段最难熬的抑制时期,最后完全断了喝酒的欲念。
上述一切都是由货币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引起的。如果货币增长率高而且稳,物价逐年上涨,譬如说10%,则经济也许能够与此相适应。大家都会预计到这10%的通货膨胀率,因而工资每年会额外提高10%,同时利率也会额外提高10%——以补偿放债人因通货膨胀而遭受的损失;税率也将按通货膨胀率调整,如此等等。
这样的通货膨胀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也没有什么用处。它只是使事情不必要地复杂化。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局面不可能很稳定。如果制造10%的通货膨胀率在政治上是有利可图的,而且也是行得通的,那么,通货膨胀率一旦达到10%,人们就会得寸进尺,进一步提高通货膨胀率,使其达到11%、12%或15%。政治上可行的目标是不要通货膨胀,而不是使通货膨胀率达到10%。这就是经验的裁决。
缓和副作用
就我们所知,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例子:通货膨胀不经过一段经济增长放慢和失业率增高的时期而结束。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经验断定,没有办法避免医治通货膨胀的副作用。
但是,缓和这些副作用,使它们来得温和一些,是可能的。
缓和副作用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事先宣布一项政策并加以贯彻实施,使之取信于民,这样一来逐渐而平稳地降低通货膨胀率。
之所以要逐渐降低通货膨胀率并要事先予以宣布,是为了给人们时间作出调整——并劝诱他们这样做。许多人是根据他们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测订立长期合同的——合同的种类很多,有关于工作的,有关于借贷的,也有关于从事某项生产或建设的。这些长期合同使我们很难迅速减少通货膨胀,而且意味着,如果试图这样做的话,会使许多人遭受严重损失。但如果给予一定时间,这些合同就会满期,或予以修改,或重新谈判其条件,到那时合同就会适应新的情况。
另一种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缓和不良的副作用的方法,是在长期合同中加进所谓“调整条款”,即合同条件将根据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自动进行调整。最常见的例子是许多工资合同中载明的生活费用调整条款。这种合同规定,每小时的工资,将按通货膨胀率或通货膨胀率的一部分再加,譬如说2%的比率增加。如果采用这种方法,通货膨胀率低,按美元计的工资增加额也低;通货膨胀率高,按美元计的工资增加额也高;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工资的购买力都一样。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财产租赁合同的。租赁合同可以规定租金逐年按通货膨胀率调整,而不规定固定的租金。零售商店的租赁合同常常是规定租金按商店总收入的百分之几计算。这种合同表面上没有调整条款,但实际上却包含有这种条款,因为商店的收入会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增加。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贷款的。贷款一般是指按一定年利率供应的、在一定时期内必须偿还的、一定数目的资金,一笔一千美元的贷款,偿还期限可以规定为一年,年利率可以规定为10%。另外的做法是不把利率规定为10%,而是规定为譬如说2%再加通货膨胀率,这样,如果通货膨胀率是5%,利率就是7%,如果通货膨胀率是10%,利率就是12%。与此相类似的另一种方法是,不把偿还的钱数规定死,而是规定要按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就上面所举的简单的例子来说,借方所欠的数额是一千美元加上通货膨胀率再加上2%的利息。如果通货膨胀率是5%,他就欠一千零五十美元;如果通货膨胀率是10%,就欠一千一百美元;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要再加上2%的利息。
除了在工资合同方面外,调整条款在美国应用得并不普遍。但其应用范围正在扩大,特别表现在抵押贷款的可变动的利率上。另一方面,在差不多所有通货膨胀率很高而且变化很大的国家,这一条款则得到了广泛应用。
这种调整条款可以缩短放慢货币增长率后调整工资及物价所需要的时间,从而缩短过渡期,减少中间的副作用。然而,调整条款虽然有用,却远不是万应灵药。要让所有合同都这样调整是不可能的(例如纸币就不能这样调整),而且这样调整许多合同代价也很高昂。使用货币的最大好处正在于能够便宜而有效地进行交易,而普遍应用调整条款将减少这种好处。最好还是没有通货膨胀,因而不需要调整条款。这就是我们主张在私营经济中运用调整条款,只作为缓和因医治通货膨胀而产生的副作用的方法,而不作为永久性措施的原因。
在联邦政府部门里,调整条款则是很可取的永久性措施。社会保险、退休金、联邦雇员的工资(包括国会议员的薪金)以及其他许多政府开支项目,现在都按通货膨胀率自动调整。但有两个很显眼的不可原谅的缺口:所得税和公债。如果按通货膨胀率来调整个人所得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率,那么,物价上涨10%也将使税率提高10%,而不是象现在这样,税率平均提高15%以上。提高税率的情况将因此而不再出现,乱征捐税的现象也会从此而绝迹。这样做,还将减少政府对通货膨胀的兴趣,因为政府从通货膨胀中得到的收入将被减少。
公债利率也完全应该按照通货膨胀率调整。美国政府自己制造的通货膨胀,使得近年来购买长期公债成了非常不上算的投资。因而在政府发行长期公债的活动中应采用调整条款,以表明政府方面对公民的公正和诚实。
人们有时把工资和物价管制当作医治通货膨胀的一种方法。近来,由于工资和物价管制已显然不能医治通货膨胀,有人又极力主张用它来缓和医治通货膨胀的副作用。据称,工资和物价管制可以起这种作用,是因为这种管制可以使公众相信,政府是认真对付通货膨胀的。人们期望,这转过来会降低人们在订立长期合同时对未来的通货膨胀率的预计水平。
工资和物价管制如果用于这一目的,将阻碍生产的发展。它使价格结构歪扭,降低价格制度运行的效率。由此造成的产量下降加重医治通货膨胀的副作用,而不是减轻副作用。物价和工资管制浪费劳动,因为它一方面歪曲价格结构,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要花在建立、执行和逃避管制上面。不论管制是强制的还是标榜为“自愿的”,后果都是一样的。
实际上,物价和工资管制几乎总是用来代替货币和财政上的节制措施,而不是用来补充这种措施。这种经验使得参加市场活动的人把实施物价和工资管制当作一种表明通货膨胀在上升而不是下降的信号,因而导致他们预测的通货膨胀率偏高,而不是偏低。
物价和工资管制在实施后的一个短时期里常常看起来是有效的。表面上,牌价即计入物价指数的价格被压低,而暗地里人们则间接提高物价和工资——如降低产品质量,取消检修服务,给工人升级,等等。但当这些规避管制的简便办法用尽之后,价格结构便被扭得越来越厉害,于是被管制的压力达到沸点,不利影响愈来愈严重,最后整个计划归于垮台。其结果是加重通货膨胀,而不是减轻通货膨胀。回顾四千年来的历史,物价和工资管制的实施,没有哪一次不是由政治家和选民的目光短浅所造成。
实例研究
日本新近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医治通货膨胀的极好范例。由图6可以看到,在日本,货币量在1971年开始以愈来愈快的速度增加,到1973年中期,年增长率达到了25%以上。
直到大约两年之后,即1973年初,才发生相应的通货膨胀。其后,通货膨胀率的急剧增长使货币政策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重点从日元的国外价值——汇率——转到它的国内价值——通货膨胀。货币的增长被急剧削减,从年增长25%以上减到10%和15%之间。这样保持了五年之久,只有些小的例外。(由于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很高,所以货币增长率保持在这个幅度内可以使物价基本稳定。就美国来说,保持物价稳定的货币增长率是3-5%。)
在货币增长率开始下降之后约十八个月,通货膨胀率也跟着下降,但直到两年半后,通货膨胀率才降到两位数以下。随后,通货膨胀率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基本保持稳定——尽管货币增长率略有上升。然后,随着货币增长率的新的下降,通货膨胀率开始迅速地趋向于零。
图里面有关通货膨胀的数据是根据消费品价格计算的,批发价格的情况甚至更好些。批发价格在1977年中期以后实际上下降了。战后,日本工人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如汽车制造业和电子工业,这意味着劳务的价格比商品的价格涨得更快。因此,相对于批发价格来说,消费品价格有所上升。
日本在放慢货币增长率后,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特别是在1974年通货膨胀率还没有对放慢了的货币增长率作出明显反应之前。然后,生产开始恢复,接着增长——虽然增长率比六十年代的繁荣时期要低一些,但仍然相当可观:每年增长5%以上。在通货膨胀率下降的过程中,日本从未实行物价和工资管制。而通货膨胀率下降时,日本正在为适应石油价格上涨进行调整。
【译者按:西方经济学家为了各种不同的目的,经常用三种方式给货币供应量下定义,分别以M1、M2和M3来表示。就美国来讲,M1包括流通的纸币、硬币和商业银行中的活期存款;M2包括M1中的各项,再加上商业银行中的定期存款,但不包括巨额存款;M3包括M2中的各项,再加上非银行储蓄机构中的存款。】
结论
我们对通货膨胀的了解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五条:
1.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起因于货币量的急剧增加,而不是产量的急速增加(虽然货币增加的原因很多)。
2.在当今世界上,政府决定——或能够决定——货币的数量。
3.只有一种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即放慢货币增长率。
4.通货膨胀的发展需要时间——以年计算而不是以月计算;通货膨胀的医治也需要时 间。
5.医治通货膨胀的不良的副作用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在过去二十年间曾四次加速货币的增长。每一次货币量以更大幅度增长后,都是经济先得到扩充,随后便出现通货膨胀。每一次当局都用放慢货币增长率的方法制止通货膨胀。货币增长率下降后,紧接着就是一次通货膨胀性的衰退。再往后,通货膨胀率下降而经济情况好转。迄今,发展的顺序同日本从1971年到1975年的经验是一样的。不幸的是,关键性的差别在于我们没有表现出日本人那样的耐心,把节制货币增长的过程延续足够长的时间。相反,我们对衰退反应过分,加快货币的增长,开始又一轮通货膨胀,因而遭受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和更高的失业率的折磨。
我们被一种虚假的两分法引入歧途:要么是通货膨胀,要么是失业。这种选择法是虚幻的。真正的选择是:较高的失业率要么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的结果,要么是医治通货膨胀的一种副作用。
本节内容概述
1.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起因于货币量的急剧增加,而不是产量的急速增加(虽 然货币增加的原因很多)。
2.在当今世界上,政府决定——或能够决定——货币的数量。
3.只有一种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即放慢货币增长率。
4.通货膨胀的发展需要时间——以年计算而不是以月计算;通货膨胀的医治也需要时 间。
5.医治通货膨胀的不良的副作用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被一种虚假的两分法引入歧途:要么是通货膨胀,要么是失业。这种选择法是虚幻的。真正的选择是:较高的失业率要么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的结果,要么是医治通货膨胀的一种副作用。
流动性偏好,手中持有货币原因:交易动机、预防动机、投机动机
温和通货膨胀的好处:引导相对价格调整、促进资源有效配置、有助于实现充分就业
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鞋革磨损成本、菜单成本、扭曲相对价格造成资源错配、发出错误的价格信号干扰人们的判断、税收扭曲
未预期到的短期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收入、财富的再分配、有利于雇主、债务人、收入灵活者
通货膨胀分类: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动型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后果:收入增加、利率提高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后果:收入增加、利率下降
第10章 潮流在转变
由于西方各国政府未能达到它们所宣布的目标,所以人们普遍起来反抗大政府。在英国,这种反抗于1979年把玛格丽特·撒切尔推上了台,她在政纲中保证她的保守党政府将完全改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历届工党政府和前任保守党政府所遵循的社会主义政策。在瑞典,1976年这种反抗导致了社会民主党在连续执政四十多年之后的败北。在法国,这种反抗导致了政策的急剧转变,打算废除政府对物价和工资的管制,并大幅度减少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在美国,这种反抗最明显地表现在横扫全国的反纳税运动中,在这场运动中,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第13号建议”,其他许多州也通过了限制州政府税收的宪法修正案。
上述反抗也许将证明是短命的,过不了多久,也许政府就会重新获得更大规模的发展。目前人们只有减少政府税收和其他捐税的热情,而没有取消政府计划——除去有利于其他人的计划——的热情。反抗大政府的情绪,是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触发的,而各国政府是能够控制这种通货膨胀的,假如它们发现这样做在政治上是有利的话。如果它们控制住通货膨胀,反抗可能会减弱或者消失。
我们认为,与其说反抗大政府的情绪是暂时的通货膨胀引起的,倒不如说通货膨胀本身部分地是这种反抗情绪引起的。当用多征税的办法增加政府开支在政治上缺乏吸引力的时候,立法者就求助于通货膨胀来增加政府开支,通货膨胀是一种无须经过表决即可征收的隐蔽赋税,一种可以随意征收的赋税。这种方法在十八世纪不受欢迎,在二十世纪也同样不受欢迎。
另外,政府计划的表面目标及其实际结果之间,在各个方面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我们在前面各章一直在进行这种对比,以至连大政府的许多最强硬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政府的失败——可是他们的解决办法几乎总是更大规模地扩大政府的作用。
一种思潮一旦迅猛高涨,它就会排除一切障碍,排除一切对立的观点。同样,当它达到顶点时,一种相反的思潮则开始上升,而且也会迅猛高涨。
直到十九世纪后期为止,占统治地位的思潮是主张经济自由和限制政府的作用,亚当·斯密和托马斯·杰斐逊为宣传和推行这种主张做了大量工作。然后,思潮转变了——部分地是由于经济自由和限制政府的作用在导致经济增长及增进大多数人的福利方面的真正成就,这些成就使那些遗留下来的各种弊病(当然有许多弊病)变得越发突出,因而引起一种要消除它们的普遍愿望。于是倾向于费边社会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的思潮迅猛高涨,这种思潮改变了二十世纪早期英国政策的方向和大萧条以后美国政策的方向。
到目前为止,上述趋向在英国已持续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在美国持续了半个世纪。这种趋向也达到了顶点。由于期望总是落空,上述趋向的理性基础已遭到破坏。它的支持者正处于守势。除了更多的老办法外,这些支持者对于消除时弊已提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他们已唤不起年青人的热情,现在年青人感到亚当·斯密或卡尔·马克思的思想要比费边社会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远为激动人心。
尽管费边社会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的潮流已达到顶点,但至今仍无明确的证据证明代替以上潮流的,将是斯密与杰斐逊主张的更大自由和限制政府作用的潮流,还是马克思与毛泽东主张的万能的、铁板一块的政府的潮流。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无论是知识分子的舆论,还是实际政策都是如此。按照过去的经验来判断,先得有舆论,然后才能有政策。
知识界舆论的重要性
在第二章中讨论过的印度和日本的例子,证明了知识界舆论的重要性,这种舆论决定着大多数人及其领导人的轻率偏见,决定着他们对于一种行动路线或另外一种行动路线的条件反射。
1867年取得治理日本大权的明治时代的领导人,主要致力于加强其本国的威力和荣誉。他们认为个人自由和政治解放没有特别的价值。他们相信贵族政治和由优秀分子实行的政治统制。可是,他们采取了自由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对民众说来导致了机会的扩大,并且在最初几十年中,这种政策还导致了更大的人身解放。另一方面,在印度取得领导权的人们,热忱地献身于政治自由、人身解放和民主。他们的目的不仅是国家的威力,而且还有公众经济条件的改善。但是,他们采取了集体主义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束缚了印度人民的手脚,不断削弱曾受到英国鼓励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获得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解放。
政策上这种差异如实地反映了两个时代不同的知识界的思潮。十九世纪中叶,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新的经济应通过自由贸易和私人企业加以组织。日本领导人大概根本没有想到要遵循任何其他路线。二十世纪中叶,人们则理所当然地认为,现代经济应通过集中控制和一系列五年计划加以组织。印度领导人或许根本没有想到要遵循任何其他路线。这两种观点都来自英国,倒是一件有趣的轶闻。日本人采用了亚当·斯密的政策。印度人采用了哈罗德·拉斯基的政策。
我们自己的历史同样有力地证明了舆论的重要性。舆论影响了一群卓越的人的工作。他们于1787年聚集在费城的独立大厅内,为他们帮助创立的新国家起草了一部宪法。他们对历史了解很深,并深受英国思潮的影响——正是这一思潮后来影响了日本的政策。他们把权力的集中,特别是集中在政府手里,看成是对自由的巨大威胁。他们起草宪法时牢记了这一点。美国宪法力图限制政府权力,保持地方分权并赋予个人以支配他们自己生活的权利。同宪法原文相比,在人权法案和宪法的前十项修正案中,上述意图更为明显:“国会不得制定确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或者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之法律”;“不得侵害人民保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用宪法中列举的某些权利取消或轻视人民的其他权利”;“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或未禁止各种行使的权力,皆由各州或人民保留之。”(摘自第一项、第二项、第九项及第十项修正案)
十九世纪后期以及进入到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美国知识界的舆论——主要处于来自英国的观点的影响之下,这类观点后来影响了印度的政策——开始发生了变化。它从相信个人责任和依靠市场转到相信社会责任和依靠国家。到了二十年代,大多数(即使实际上不是大多数,也是强有力的少数)关心公众事务的大学教授都持有社会主义观点。《新共和》周刊和《民族》双周刊是当时最主要的表达知识界见解的两种杂志。由诺曼·托马斯领导的美国社会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其主要力量却在大专院校里。
我们认为,在二十世纪前几十年中,社会党是美国最有影响的政党。因为它没有希望在全国范围取得选举胜利(不过也确实有少数社会党人当选为地方官员,尤其是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市),它成了一个坚持原则的政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则不是这样。为了把根本互不相关的各种派别和各种利益集团结合到一起,民主党和共和党成了搞权宜之计和妥协的政党。它们不得不避免“极端主义”,保持中间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说它们是完全一样的两个政党——但实际上它们不同的地方确实很少。不过,最后这两个主要政党都采取了社会党的立场。社会党得到的总统选票从未超过6%(1912年尤金·德布斯所得)。它1928年得到的选票不到1%,1932年仅为2%(诺曼·托马斯所得)。可是,该党1928年总统竞选政纲里的几乎每项经济政策,现在都被法律固定了下来。
一旦知识界舆论的变化影响到更广大的公众,正象大萧条后发生的情况那样,在一种大不相同的舆论影响下制定的宪法,证明至多只能推迟政府权力的增长,而不能阻止政府权力的增长。
用社利先生的话来说,“不论是否符合宪法精神,最高法院都可以自由解释宪法。”宪法的词句被重新解释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那些旨在阻止政府扩张权力的词句遭到漠视。正如雷奥尔·伯杰在仔细考察最高法院对一项修正案的解释时写道的:
最高法院对第十四项修正案的解释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了最高法院如何“行使”哈兰法官所说的“修正权”,也就是在解释含义的名义下不断修改宪法的权力。……
可以有把握地说,最高法院无视宪法制订者的意愿,对宪法作了完全违反原意的转释。……
这样的行为使人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最高法院的法官就是法律。
思潮和人民的行为
费边社会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的思潮已达到顶点的证据,不仅来自知识分子的著作,来自政治家们在竞选讲坛上表明的观点,而且也来自人民行为的方式。他们的行为无疑受到思潮的影响。反过来,人民的行为也加强着这种思潮,并且在把这种思潮变成政策的过程中起着较重要的作用。
正如A.V.迪塞以卓越预见于六十多年以前写道的:“假如社会主义立法的进展受到抑制,这种挫折与其说归因于任何思想家的影响,不如说是归因于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某些明显事实,例如增税显然是社会主义政策通常的伴随物,假如不是永恒的伴随物的话。”通货膨胀、高额税率以及工作效率明显低下、官僚统治和来自大政府的过多管制,都在发挥迪塞所预期的作用。所有这一切迫使人民不得不自己管理自己,不得不想办法绕过政府设置的各种障碍。
帕特·布雷南在1978年成了有几分名气的人,因为她和她丈夫同美国邮政局展开了竞争。他们在纽约的罗彻斯特的一间地下室里开始了营业,保证把投寄罗彻斯特商业区的包裹和信件于他们收到的同一天送到指定地址,收费标准低于国家邮政局的标准。他们的营业很快兴旺起来。
毫无疑问,他们违犯了法律。邮政局到法院控告他们,这场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他们失败了。当地的企业家曾给予他们财政上的支持。
帕特·布雷南说:
我想人民将进行一种温和的反抗,或许我们就是这种反抗的开端。……你看到人民在反对官僚,若干年以前你不能想象会这样做,因为你会受到镇压。……人民决定:他们的命运是属于自己的,而不属于在华盛顿的毫不关心人民的人。因此,这不是搞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而是人民重新考虑官僚们的权力并且对它加以抵制的问题。……
在各行各业中,人们又提出了自由的问题——你是否有权利从事某种职业,以及是否有权利决定怎样从事这种职业。在消费者利用他们认为是廉价的和优良得多的服务方面,也有自由的问题,按照联邦政府的看法以及被称为私人快速邮递法令的法律正文,我没有自由开办一个企业,消费者也没有自由去利用它——在我们这样一个完全以自由和自由企业为基础的国家中会发生这种事情,怎么能不令人感到非常奇怪呢。
帕特·布雷南对其他人企图控制她的生活作出了人人皆有的正常反应,因为她认为她的生活与他们毫不相干。最初的反应是忿恨;随后便试图用合法的方式绕过各种障碍;最后是对法律的蔑视。这个最后的结果是可悲的,但却是不可避免的。
在英国,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人们对没收性赋税作出的反应。英国的一位权威人士格雷厄姆·特纳说道:
我认为,可以完全公平地说,在最近十或十五年的过程中,我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弄虚作假者的国家。
人们是怎样弄虚作假的呢?人们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做到这一点。让我们先从最低阶层谈起。且以乡下的一个小杂货商人为例。……他是怎样赚钱的?他发现通过正式的批发商进货,他得经常使用发票,可是如果他现购自运,……商品的利润额便可以逃税,因为税务稽查员根本不知道他已拥有这些商品。这就是他赚钱的办法。
现在让我们来看最高阶层的情况,例如公司董事,他们使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方法弄虚作假。他们通过公司购买食品,以出差的名义度假,安排自己的妻子当公司董事,即使她们从未到过工厂,他们利用公司的材料为自己盖住宅,方法简单得很,就是在公司建造厂房时动手盖住宅。
从下到上,从干着极卑微工作的劳动阶级一直到最上层——企业家、高级政治家、内阁成员、影子内阁成员——都在弄虚作假。
我认为几乎每个人现在都感到,税收制度非常不公平,而且每个有办法的人都试图找到一种方法躲过税收制度。因为现在人们一致认为税收制度不公平,所以国家事实上变得有点象阴谋集团——大家互相帮助去弄虚作假。
你在这个国家里弄虚作假是没有困难的,因为其他人实际上愿意帮助你。可在十五年以前情况是全然不同的。人们会说,嗨,怎么会出现这种完全不应该有的事呀。
《华尔街日报》(1979年2月1日,第18页)曾刊登过梅尔文·B.克劳斯撰写的一篇题为“瑞典人的抗税”的文章,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这篇文章中以下的内容:
针对西方最高的赋税开展的瑞典革命,是以个人的首创精神为基础的。瑞典老百姓不是依赖政治家,而是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干脆拒绝纳税。有几种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其中一些办法是合法的。……
瑞典人拒绝纳税的办法之一是少干活。……在斯德哥尔摩美丽的多岛屿的海上坐船游览的瑞典人,生动地说明了这个国家秘密的赋税革命。
瑞典人运用亲自动手的办法逃避纳税。……
物物交换是瑞典人逃避高额赋税的另一种办法。要诱使一个瑞典牙医离开网球场坐在他的诊所里给病人看病,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可是一个患牙疼的律师却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作为回报,律师可为牙医业务提供法律服务。进行物物交换使牙医节省了两笔税款:他本人的所得税和应为律师酬金缴纳的税。尽管物物交换本来是原始经济的标志,但瑞典的高额赋税却使得它在这个福利国家,特别是在各种专门职业中成了一种受人欢迎的交易方式。……
瑞典的赋税革命不是富人的革命。在各个收入阶层都在发生这种革命。
瑞典这个福利国家正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它的思想体系促使政府不断增加支出。……可是,对于瑞典公民来说,赋税负担则有其饱和点,一旦达到饱和点,他们就会起来反对进一步增税。……瑞典人抵制高额赋税的方法,有损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日益增长的政府支出是在挖福利经济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的墙脚。
为什么特殊利益占优势
如果费边社会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的潮流已达到顶点,继之而来的不是极权主义社会,而是较为自由的社会和权力较为有限的政府,那么,公众不仅必须承认当前状况的缺陷,而且必须认清这种状况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为什么政策的目标很好,而结果常常适得其反?采用什么方法能阻止这一进程,或者使它倒转过来?
集中在华盛顿的权力
每当我们来到我国首都华盛顿的时候,都对集中在这个城市里的巨大权力惊叹不已。漫步在国会大厦,我们很难看到那四百三十五名众议员和一百名参议员,因为这里有一万八千名政府雇员,平均每个参议员约有六十五名雇员,每个众议员约有二十七名雇员。另外,还有一万五千多名正式的院外活动集团成员,身后经常跟着秘书、打字员、调查研究人员或者他们所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在国会大厦里串来串去,伺机施加影响。
而这仅仅是冰山之巅。联邦政府雇用着近三百万文职人员(不包括穿军服的武装力量)。有三十五万人以上在华盛顿以及附近的郊区工作。还有无数人间接地被政府雇用,雇用他们的是同政府订有合同的名义上的私人机构。另有一些人被劳工组织或资方组织或其他特殊利益集团所雇用,这些组织或集团都在华盛顿设有自己的总部或者至少设有一个办事处,因为华盛顿是政府所在地。
对律师们说来华盛顿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全国许多最大的最富有的法律事务所都设在这里。据说在华盛顿仅在联邦机构或管制机构中工作的律师就有七千多名。一百六十多家其他地方的法律事务所在华盛顿设有办事处。
和苏联、赤色中国或邻近美国的古巴等集权主义国家的权力不同,在华盛顿的权力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铁板一块的权力。权力被分割为许许多多的小块。全国各地的每一个特殊利益集团都试图尽可能地把它们的手伸到力所能及的不管什么样的权力上面。其结果是,政府几乎在每个问题上都脚踏两只船。
例如,在华盛顿的一座大楼里,一些政府雇员正在整天工作,试图制订和执行各种计划,用我们的钱劝阻人们不要吸烟。而在另一座距离不太远的大楼里,另外一些同样具有献身精神并且同样努力工作的雇员,整天工作以便用我们的钱补助农场主们去种植烟草。
在一座大楼里,工资与物价稳定委员会正在加班加点工作,试图用软硬兼施、连蒙带吓的方法迫使企业家降低产品价格,并用同样方法迫使工人降低他们的工资要求。而在另一座大楼里,农业部的某些下属机构则正在执行各种计划,以维持或提高食糖、棉花以及其他许多农产品的价格。在另外一座大楼里,劳工部的官员们根据戴维斯-培根法案,正在确定所谓“普遍实行的工资”,以此提高建筑工人的工资率。
国会建立了一个雇用二万名职工的能源部,以促进能源的保护。国会还建立了一个雇用一万二千名以上职工的环境保护局,它颁布了各种规章制度和命令,其中大部分要求使用更多的能源。无疑,在每一个机构里面,又各有一些下属单位,它们的工作目的也是互相矛盾的。
如果造成的结果不是如此严重的话,所有这一切似乎是非常荒唐可笑的。虽然上述各种机构的许多作用可以相互抵消,但它们的花费并不能相互抵消。每一个计划都要从我们口袋里掏钱,这些钱我们本来可以用来购买满足我们各种需要的商品和劳务。每一个机构都使用着能干的、技术熟练的人员,这些人员本来可从事生产性活动。每一个机构都挖空心思制订出各种条例、规则、繁琐的办事程序和需要填写的表格,这一切都在折磨着我们大家。
集中起来的利益与分散的利益
权力的分散和各项政府政策的相互矛盾,其根源在于民主制度的政治现实,这一制度是通过制订详细而具体的法律而运转的。这样一种制度往往把过大的政治权力赋予利益高度集中的小集团;往往比较重视政府行动的明显的、直接的和即刻显示出来的效果,而不重视政府行动的可能更重要的但却是隐蔽的、间接的和迟缓的效果;往往为了特殊利益而牺牲普遍利益,而不是相反。在政治生活中似乎也有一只无形之手,其作用恰好与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之手的作用相反。本意想要普遍利益的人们,受这只无形的政治之手的指引,促进了并非他本意想要促进的特殊利益。
这个问题的性质只需举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让我们先来看政府帮助海运业的计划,该计划的内容包括向船舶建造和营运业务提供补贴,以及限定大部分沿海运输业务由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来经营。据估计纳税人每年为该计划支付的费用大约六亿美元——或者换句话说,纳税人每年要为积极从事这一行业的四万人当中的每个人花一万五千美元。船舶所有者、经营者以及他们的雇员,受到强烈刺激去获得并保持这个份额。他们毫不吝惜地出钱对议员进行游说以及捐助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六亿美元分摊到二亿多人口上,平均每人每年出三美元,一个四口之家每年出十二美元。我们当中有谁会投票反对一个国会议员候选人,只因为他把上述费用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当中到底有多少人认为值得花钱挫败上述措施,或者甚至认为值得花时间了解这类事情?
另一个例子是,各钢铁公司的股东们、这些公司的总经理们以及钢铁工人都很清楚地知道,钢铁进口量的增加,对他们说来将意味着收入下降和工作机会减少。他们很清楚,政府排斥进口的行动会给他们带来好处。而出口行业的工人则不知道他们的工作受到了威胁。他们将失掉工作,因为减少从日本的进口必然减少对日本的出口。当他们丢掉工作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会丢掉工作。汽车或厨房的火炉或其他钢铁制品的买主们,可能抱怨他们不得不付较高昂的价格。限制钢铁进口迫使工厂主采用高价的国产钢铁以代替低价的外国钢铁;但有多少买主会把价格的提高追溯到这种限制呢?他们责备的对象很可能是“贪得无厌的”工厂主或者“得寸进尺的”工会会员。
农业是另一个例子。农场主们为了获得提价的支持,开着拖拉机来到华盛顿游行示威。政府作用的变化使得他们出现在华盛顿成了自然的事情,在此以前,他们只会责怪恶劣的气候,到教堂祈祷,而不是去白宫寻求帮助。甚至对于象食品这样必需和明显的产品说来,在华盛顿也没有消费者游行以抗议支持提价。尽管农业是美国的主要出口行业,农场主们并没有认识到事情到了这一地步是政府干预对外贸易造成的。例如,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他们可能因限制钢铁进口而受到损害。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完全不同的即有关美国邮政局的例子。解除政府对第一类邮件(即不受检查、邮资最贵的密封邮件)垄断的每一个行动,都遭到了邮政工人工会的坚决反对。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对私人企业开放邮政业务可能意味着他们会丢掉工作。防止出现这种结局对他们是有利的。正如罗彻斯特的布雷南夫妇经营邮政业务的实例所表明的,如果废除政府对邮政事业的垄断,将会出现一个生气勃勃的私人邮政行业,该行业将由几千家企业所组成,雇用几万名工人。那些可能在这样一种行业里找到好工作的人,几乎没有一个知道废除国家垄断会使他们找到好工作。他们肯定不会去华盛顿向有关的国会委员会作证。
一个人从某一项与他有特殊利益的计划中获得的好处,可能不足以抵偿对他有轻微影响的许多计划使他付出的代价。可是,对他有利的却是支持某一项计划,而不是反对其他计划。他很容易看到,他和具有同样特殊利益的小集团,花得起足够的金钱和时间促使对他们有利的计划得以通过。不促进对他有利的计划,并不会阻止其他对他有害的计划被采用。要做到这一点,他得象主持自己的计划那样,竭尽全力反对其他每一项计划。这显然是一桩赔本的买卖。
公民们是注意赋税的——可是就连这种注意也因多数赋税的隐蔽性质而被分散了。公司税和货物税包括在人们购买的商品价格之内,而没有单独的账目。大部分所得税在发工资以前就被扣除了。通货膨胀是最为恶劣的隐蔽赋税,不容易被人理解。只有销售税、财产税和超过扣除额的所得税,能够直接被人痛苦地感觉到——人们所怨恨的正是这些赋税。
官僚机构
政府的单位越小以及分派给政府的职能所受到的限制越多,政府的活动不反映普遍利益而反映特殊利益的可能性就越少。新英格兰的市镇会议是我们所想到的典型。被治理的人民了解而且能够控制进行治理的人们;每一个人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议事日程很小,以致每一个人不仅十分了解大事项,而且也十分了解小事项。
随着政府活动范围和作用的扩大——不论是由于统治面积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还是由于职能范围的扩大——在被治理的人民与进行治理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将变得越来越少。任何一部分公民都不可能十分了解大大扩大了的政府议事日程上的全部事项,甚至不可能十分了解所有主要事项。管理政府所必需的官僚机构成长起来,它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全体公民及其选出的代表们之间。官僚机构既是特殊利益集团借以实现其目标的一种工具,同时本身又是一个重要的特殊利益集团——即第五章中提到的新阶级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目前在美国,只是在乡村、市镇、小城市以及大城市的郊区,说得上公众可以有效而具体地控制政府——而即使在这些地方,公众对政府的控制也只限于那些不是由州和联邦政府委托管理的事情。在各大城市、各个州府和华盛顿,人民的政府不是由人民来控制,而是由不经常露面的官僚集团来控制。
可以想象,没有哪个联邦议员能够看一遍他必须进行表决的所有法令,更不用说分析和研究这些法令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必然要依靠他的许多助手、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议员同事、或者某些其他提供消息的人,来决定如何表决。目前,对于制定具体法令来说,未经选举产生的国会中的官僚肯定要比选举产生的议员具有大得多的影响。
在实施各项政府计划方面,情况甚至更为严重。广泛分布在政府各部门和各种独立机构中的官僚,确实不受公众选出来的代表控制。选举产生的总统、参议员和众议员此来彼去,但文职人员却保留不动。高级官僚非常老练地运用拖拉的办事程序来耽搁和破坏他们不赞成的计划;他们善于以“解释”法令为名颁布各种条例和规章,这些解释事实上巧妙地、有时赤裸裸地改变了原法令的意图;他们善于拖延执行他们不赞成的法令,同时加紧执行他们赞成的法令。
最近,面对日益复杂的和影响广泛的立法,联邦各法院已不再充当公正解释各项法令的传统角色,而是积极参与制定法令和实施法令的工作。因此,它们变成了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而不是斡旋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一个独立部分。
官僚们没有篡夺权力。他们没有故意参与任何一种破坏民主程序的阴谋。权力被强加到他们头上。除了赋予职责外,以任何其他方法从事复杂的政府活动,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当这一做法在负有不同职责的官僚们之间引起冲突时——例如,最近在被委派去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官僚与被委派去促进能源的保护和生产的官僚之间就发生了冲突——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授权另一批官僚去解决冲突——据说,当真正的问题不是拖拉的办事程序而是有吸引力的各种目标之间的冲突时,只要减少拖拉的办事程序就行了。
被赋予职责的高级官僚们,不能设想他们提出或接到的报告、他们参加的会议、他们同其他重要人物进行的冗长的讨论、他们颁布的规章制度——所有这些都是问题本身,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不可缺少的,认为自己比无知的选民或自私自利的企业家更知道应该做些什么。
官僚机构的规模和权力的增长,影响着公民和其政府之间关系的每一个细节。如今如果你有冤屈或者你能从政府措施中发现获取利益的办法,你首先采用的方法很可能是对某个政府官员施加影响,使他作出有利于你的裁决。你也可能求助于你选出的议员,但你求助于他,是要他与一名政府官员相串通,好替你说话,而不是要他支持某项法案。
要办好企业越来越依赖于熟悉华盛顿的情况,依赖于能够影响议员和政府官员。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出现了所谓“旋转门”。在华盛顿当一个时期的官,已成了企业家办好企业必经的学徒期。谋求政府职位,很少是要在政府内干一辈子,而是想同将来可能成为雇主的政府建立联系,了解其内情。虽然防止公务人员舞弊的法律急剧增加,但它们至多只是阻止了人们明目张胆地舞弊。
当某一特殊利益集团试图通过惹人注意的立法活动为自己谋取利益时,它不仅必须给它的要求装点上普遍利益的词句,而且必须使相当一部分不感兴趣的人相信它的要求对公众是有好处的。被认为是明显自私自利的议案很少被通过——例如,虽然卡特总统在得到有关工会对竞选运动的巨大帮助以后表示赞同给海运业以更多特权,但这一企图最近却遭到了失败。保护钢铁工业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据说有利于国家安全和充分就业;向农业提供补贴,据说可以确保食品的可靠供应;国家垄断邮政事业,据说可以加强整个国家的团结,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近一个世纪以前,A.V.迪塞说明了为什么打着普遍利益幌子的花言巧语具有如此巨大的说服力:“州政府的干预,特别是采用立法形式的干预的有益效果,是直接的、立竿见影的,并且可以这样说,是显而易见的,而它的有害效果则是间接的、渐进的,是看不到的。……因此,大多数人必然过于偏爱政府干预。”
当某一特殊利益集团不是通过立法活动而是通过行政程序谋求利益时,戴斯所说的对政府干预的“自然偏爱”便会大大加强。一家卡车运输公司为了得到有利的裁决而求助于州际商务委员会时,往往也打着促进普遍利益的幌子,但谁也不会戳穿这个谎言。除了政府官员外,该公司无需说服任何人。反对意见很少来自那些关心普遍利益而与卡车运输业无关的人。反对意见来自其他有关各方,如托运人或其他卡车运输公司,他们也有自己的打算。披上的伪装确实是薄薄的一层。
法院作用的变化,使官僚机构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发展嘲弄了约翰·亚当斯在马萨诸塞州的宪法草案(1779年)中表达的理想,即建立“一个由法律支配的而不是由人支配的政府”。凡是从国外旅行回来接受过海关彻底检查的人,凡是让国内收入署审核过税单的人,凡是接受过职业安全和卫生管理局的一名官员或联邦各种机构的一大堆官员检查的人,凡是要求过政府机构给予裁决或给予营业执照的人,凡是在工资和价格稳定委员会面前为提高价格或工资作过辩护的人,总之,凡是同政府官员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美国到底有多少法治可言。政府官员理应是我们的仆人。当你隔着办公桌坐在正审核你的税单的国内收入署代表的对面时,究竟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呢?
让我们来看另一个例子。《华尔街日报》(1979年6月25日)最近一篇报道用的大标题是:一家公司的“前任经理支付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费用”。据报道,这位前任经理莫里斯·G.麦吉尔说:“问题不在于我本人是否从这笔交易中得到了好处,而在于一个卸任的经理的责任是什么。打官司是会引起兴趣的,可我却决定不打官司就付清费用,这完全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同证券交易委员会斗争到底的代价是巨大的。”不论胜败麦吉尔先生都必须支付诉讼费。而证券交易委员会内负责同他打官司的那位官员,除了在同事中的声誉会受到影响外,不论打胜还是打败,同他自己都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能够做什么
不用说,凡是想阻止或扭转目前这种趋势的人,都应该反对进一步扩大政府权力和职责范围的新措施,应该促使现有措施的废除和改革,而且应该选出具有这种观点的议员和行政官员。但这不是扭转目前趋势的有效方法。这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会保卫自己的特权,并试图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对政府进行限制。我们面对的将是一条九头蛇,它长出新的头能比砍掉旧的头还快。
我们的开国元勋已经给我们指出了一种较为有希望扭转目前趋势的方法:可以说是搞一揽子交易。我们应该采用自我克制的各种法令,以限制我们企图通过政治渠道追求的目标。我们不应该按照其是非曲直考虑每件事情,而应该制定广泛的规章和条例以限制政府的活动范围。
这种方法的优点已被宪法的第一项修正案很好地说明了。相当一部分议员和选民也许会赞成对言论自由施加某些限制。大多数人很可能赞成禁止纳粹分子、耶稣七日再生派教徒、“耶和华的见证人”派教徒、三K党、素食主义者或任何其他小集团在街头巷尾发表演讲。
第一项修正案的高明之处在于它采用了一揽子交易的方法。该修正案用的普遍原则是:“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之……法律”;它没有按照是非曲直考虑每件事情。大多数人那时支持了它,而我们相信大多数人今天仍然会支持它。当我们处于多数人的地位时,对别人的自由受到干涉,我们每人的感受远远不如自己处在少数人的地位时,不让自由受到干涉来得深切——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总有处于少数人的地位的时候。
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有一项与宪法的第一项修正案相同的法案,来限制政府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权力——一项经济上的“人权法案”,以补充和加强原来的“人权法案”。
把这样一种“人权法案”并入我国的宪法中,这件事本身并不会自行扭转政府越来越大的趋势,或防止这种趋势重新得到发展——它的作用肯定不会超过宪法本身。我国的宪法未能阻止政府权力的增长和集中,以致政府权力的增长和集中远远超出了宪法制定者允许或设想的界限。对于发展和保护一个自由社会来说,一部成文宪法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虽然英国经常只有“不成文”宪法,但它却使自由社会得到了发展。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采用了事实上从美国宪法逐字照抄过去的成文宪法,但它们并没有建成自由社会。一部成文的——或者与此有关的不成文的——一宪法要发挥效力,它必须在一般公众及其领导人中间得到普遍的舆论支持。该宪法必须体现人们已经深信的各项原则,这样,行政部门、立法机关和法院的行为才会自然而然地符合这些原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舆论发生变化时,政策也将随之变化。
然而,我们认为制定和投票通过经济上的“人权法案”,将最有效地扭转政府越来越大的趋势,其原因有二:第一,制定修正案的过程会对制造舆论起很大的帮助;第二,同现在的立法程序相比,颁布修正案将更为直接、更为有效地使上述舆论变成实际政策。
假定赞成新政自由主义的思潮已经达到顶点,那么,在制定这样一个“人权法案”的过程中将会引起全国性的争论,这场争论肯定会使人们的思想转向自由,而不是转向集权主义。这场争论将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大政府的问题及其可能的医治方法。
采用这类修正案的政治过程,将比我们现在的立法和行政结构更为民主,因为它使一般公众得以决定事态的结果。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人民的政府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志行事。每一次民意测验都表明,绝大多数人反对为调整学生中的种族比例用校车接送学生——可是不仅继续用校车接送学生,而且还不断推广这种做法。在就业和高等教育方面实施的种种调整种族比例的行动计划,以及根据结果平等的思想采取的其他许多措施,情况也都是这样。就我们所知,搞民意测验的人从来没有向公众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你的40%以上的收入由政府替你花费,你是否得到了所付款项的等价物?”对于民意测验的结果,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
由于上一节列举的原因,特殊利益集团是在牺牲普遍利益的情况下获得成功的。在大学、新闻单位、特别是联邦官僚机构中成长起来的新阶级,已经成了最有势力的特殊利益集团之一。它不顾公众的普遍反对,并且经常不顾有关法令的约束。总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别人头上。
采用修正案具有加强地方分权制的巨大效能。它要求四分之三的州分别采取行动。甚至新的修正案的提出可以越过国会:宪法第五条规定“国会……应三分之二的州议会的请求,将召集会议以提出修正案。”到1979年中期,已有三十个州要求国会召开会议,以提出要求联邦预算保持平衡的修正案。再有四个州议会提出这种要求,即可达到召开会议所必需的数目,这一前景在华盛顿已经引起了极大惊慌——其原因是:这样一来,华盛顿的官僚机构就被抛在一边。
限制税收和政府开支
采用宪法修正案来限制政府的运动,在税收和政府开支方面已经开展起来了。到1979年初,已经有五个州正式通过了本州宪法的修正案,修正案限制了州政府可以征收的赋税总额,一些州还限制了州政府可以开支的经费总额。同样性质的修正案,在其他一些州中已做好了正式通过的准备工作,在另外一些州里则预定在1979年选举中提出来进行投票表决。剩下的一些州有半数以上正在积极准备通过这类修正案。同我们有联系的一个全国性组织“全国税收限制委员会”(NTLC),作为情报交换所和某几个州的行动协调者正在起作用。1979年中期,该组织在全国拥有约二十五万名会员,而且会员人数正在急剧增加。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有两项重要的事态发展。一个是各州议会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去委托国会召集全国性会议以提出平衡预算的修正案——这最初是由全国纳税人联盟发动的,该联盟于1979年中期在全国拥有的会员超过十二万五千人。另一事态发展是,人们要求通过限制联邦开支的修正案,该修正案是在全国税收限制委员会倡议下起草的。起草委员会(我们两人都是该委员会委员)包括了律师、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州议员、企业家以及各团体组织的代表。该委员会起草的修正案已被提交给了国会参众两院,全国税收限制委员会正在开展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来支持它。
在州和联邦两类修正案背后的基本思想,是纠正我们现有结构中的缺点,在这种结构下面,民主选出的议员,投票赞成的开支数额要多于大部分选民认为合适的数额。
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上述结果是由赞成特殊利益的政治偏见造成的。目前确定政府预算的办法,是把批准用于各项计划支出加在一起。与某项计划有特殊利益的少数人,花钱并努力活动使该计划得以通过;而大多数人即使对该计划有了解,而且每个人要为计划支付若干美元,也不会认为花钱或努力活动反对该计划是合算的。
多数人的确在实行统治。但这是有点特殊性质的多数。它是由许多具有特殊利益的少数人的集团构成的。当选国会议员的方法,是把各占你的选民的,比如说,2%或3%的诸集团集中起来,这些集团中的每一个集团都强烈地关心着一个特殊问题,该问题同你的其余选民几乎没有关系。假如你答应支持某个集团的问题,它将乐意投你的票,不管你对其他问题持何种态度。把足够的这类集团集合起来,你将拥有51%的多数。这就是统治着我国的互投赞成票的多数。
上面提出的修正案将限制议员——不论是州议员还是联邦议员——受权拨付的款项总额,从而改变议员起作用的条件。这些修正案将预先限定政府的预算,就象我们每一个人的预算都受到限制一样。许多与特殊利益有关的立法是不值得追求的,但它们的坏处决不至于那么明显,也并不是那么一无是处。相反,每一种措施都将被描述为服务于一个高尚的目标。问题是高尚的目标太多了,数也数不尽。当前,议员在反对“高尚的”目标方面往往处于劣势。假如他提出反对的理由,说某一高尚的目标将提高税收,那他将被扣上反动分子的帽子,说他为了卑鄙的唯利是图的原因而不顾人民的需要——毕竟,这个高尚的目标将只需要把每个人的税款提高几美分或几美元。这个议员将处于有利得多的地位,如果他能够说:“不错,你的目标是高尚的,可是我们的预算是有限的。为你的目标花更多的钱意味着为减少其他目标得到的钱。这些目标当中哪一个应该被削减?”结果将会要求各个特殊利益集团,为了从一个固定的馅饼中分得较大份额而彼此竞争,而不是他们能彼此勾结起来牺牲纳税人的利益,把馅饼做得越来越大。
因为各州无权印制钞票,所以州政府的预算可以通过控制可征收的税款总额加以限制,这是各州已经正式通过或者已经提出的大多数修正案业已采用的方法。联邦政府能够印制钞票,因此限制税收不是一种有效的办法。这就是我们的修正案为什么要限制联邦政府的总开支的原因,而不论资金是怎样筹集的。
限额——不论是对税收还是对政府开支——将主要根据州或全国的总收入来规定,如果政府开支等于限额,政府的开支作为收入的一部分将保持不变。这将阻止政府越来越大的趋势继续发展,而不是扭转这种趋势。然而,限额也将有助于扭转政府越来越大的趋势,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如果哪一年的政府开支不等于限额,则适用于以后年份的限额会更低。而且,提出的联邦修正案要求降低政府开支在州或全国的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如果通货膨胀年率超过3%的话。
其他宪法条款
我们收入中政府所花费的那一部分的逐渐减少,对于建立一个较为自由、较为强大的社会来说,将是重要的贡献。但这仅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步骤。
政府对我们的生活进行的许多最有破坏性的管理,并不要政府花许多钱,例如:征收关税,实行物价和工资管制,颁发职业执照,对工业实行管制,颁布保护消费者的法令等。
对付所有这些政府管制的最有成效的方法,同样是颁布限制政府权力的一般性法规。到目前为止,制定适当法规的工作仍未受到人们的重视。任何法规在其能被认真地采用以前,需要由具有各种不同利益的人进行的彻底审查,需要限制税收和政府开支的修正案已得到的那种认识。
作为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我们概述一下看来是合乎需要的几项修正案。我们强调这些例子是尝试性的,主要目的是在这一基本尚未探索过的领域中,激励进一步的思考和进一步的工作。
国际贸易
宪法现在规定:“未经国会同意,各州不得对进口商品或出口商品课以任何进口税或出口税;惟在执行该州之检查法律上有绝对必要者,不在此限。”修正案可能规定如下:
国会不得对进口商品或出口商品课以任何进口税或出口税,惟在执行其检查法律上有绝对必要者,不在此限。
以为现在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修正案,那是不切实际的。然而,要通过废除个别关税获得 贸易自由,如果说有不同之处的话,则是更加不切实际。对全部关税采取措施,可以使我们大家作为消费者的利益联合起来,以反对我们作为生产者分别具有的那种特殊利益。
工资和物价管制
正如我们在几年前写道的:“假如美国有一天屈服于集体主义,屈服于政府对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管制,那将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者在论战中取得了胜利,而是因为工资和物价管制。”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指出的,价格传送消息——沃尔特·里斯顿通过把价格描述为言论的一种形式,已经非常恰当地解释了这一点。而在自由市场上决定的价格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在此我们需要有同宪法的第一项修正案极为相似的条文:
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以剥夺商品或劳务的卖者对其产品及劳务定价的自由。
职业执照的颁发
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比我们可能从事的工作对我们的生活具有更大的影响。在这个领域里 放宽自由选择就要求限制各州的权力。在此,我们需要有我国宪法正文里禁止各州采取某些行动的条款,或者是第十四项修正案。一个建议是:
各州不得制定或施行剥夺合众国公民从事他所选择的工作或职业的权利的任何法律。
多用途的自由贸易
修正案前面的三项修正案可以由一项修正案来代替,这项修正案可以仿效我国宪法的第二项修 正案(它确保人们保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人们在相互同意的条件下买卖合法的商品和劳务的权利,国会和任何州均不得侵犯之。
税收
按照一致同意的看法,个人所得税亟需改革。据说这种赋税根据“支付能力”征收的,对富人较重而对穷人较轻,并且考虑到了每个人的特殊情况。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税率在官方文件上被分成许多等级,从14%到70%。然而税法的漏洞如此之多,特免规定又五花八门。以致高额税率差不多完全成了装璜门面的东西。对高于个人免征额的全部收入(除真正的职业开支外,不允许有其他扣除),实行一种一刀切的低额税率——低于20%——会比现有不实用的结构给政府带来更多的收入。纳税人的境况会好一些——因为他们可以省掉因避免所得税而花的费用;经济情况也会好一些——因为税收考虑在资源分配中将起较小的作用。唯一吃亏的人是律师、会计、文职人员以及议员们——他们将不得不从事比填写各种税单、发现税收漏洞并且试图堵塞漏洞等工作更富有成效的活动。
公司所得税也是有很大缺点的。它是一种隐蔽的赋税,公众在所购买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中不知不觉地纳了税。这种赋税对公司所得征两次税——一次是对公司课税,一次是收入分配后对股东课税。它不利于资本投资,从而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它应该被废除。
尽管左派和右派一致认为,应该降低税率,减少漏洞并取消双重课税制,但这种改革却不能通过立法程序来完成。左派担心假如他们同意较低的税率和较少的纳税等级以换取消灭漏洞,新的漏洞不久就会出现——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右派担心假如他们同意消灭漏洞以换取较低的税率和较少的纳税等级,更不合理的纳税等级不久就会出现——他们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例,说明只有宪法修正案可以使各方达成体面的妥协。这里所需要的修正案必须废除现有的批准所得税的第十六项修正案,而代之以下面一段话:
国会有权课征个人所得税,不必问其所得之来源,其收入不必分配于各州,亦不必根据人口普查与统计,只是必须对超过职业与商业开支以及固定数额的个人津贴的一切收入施以同一税率。“个人”一词不包括公司和其他法人。
稳定的货币
当初颁布宪法时,国会被授权“铸造货币,厘定本国货币及外币之价值”,指的是商品货币:说明美元应为一定克数重量的白银或黄金。美国革命期间以及更早一些时候各殖民地内纸币的膨胀,使得宪法制订者否定各州有权“铸造货币;发行信用票证(即纸币),使用金银币以外之物以作清偿债务的货币。”宪法未说明国会是否有权批准政府发行纸币。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根据第十项修正案的规定,政府发行纸币是违反宪法的。第十项修正案规定“本宪法所未授予合众国……之权力,皆分别由各州或由人民保留之”。
南北战争期间,国会授权政府发行美钞,并宣布美钞为偿付一切公私债务的合法货币。南北战争以后,在一系列有关美钞的著名讼案中,最高法院在审理第一个讼案时曾宣布发行美钞是违反宪法的。“使人摸不着头脑的是,这项裁决是由首席法官萨蒙·P.蔡斯公布的,正是在他担任财政部长时发行了第一批美钞。他不仅公布了这项裁决,而且还以首席法官的身份,宣布自己应对担任财政部长时的违反宪法的行为负责。”
随后,扩大了的和重新组成的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多数推翻了第一个决定,断言使美钞成为合法货币是合乎宪法的,首席法官蔡斯当时是持反对意见的法官之一。
恢复金币本位制或银币本位制既行不通也不合乎需要,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使货币保持稳定。目前最好的方法,是要求货币当局把货币数量的增长率保持在一个固定的变动范围之内。修正案的起草是格外困难的,因为它同有关的制度结构联系非常紧密。修正案也许应该这样写:
国会有权批准政府以通货或记帐的形式发行无息债券,如果流通中的美元总额的年增长率不超过5%和不低于3%的话。
也许应该附带这样一条规定,即如果爆发战争,从而使政府停止或延期支付每年应清偿的债务时,国会参众两院各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或者同样有资格的多数,可以撤销上述要求。
免遭通货膨胀的损害
假如前面一项修正案被通过并被严格执行,那将结束通货膨胀并确保物价水平相对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将不需要采取其他措施来阻止政府未经允许而随意征税,因而也就不存在因征税而引起的通货膨胀。然而,那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得到人们广泛支持的,将是使政府搞通货膨胀无利可图的修正案。它比一个较为专门和容易引起争论的稳定货币的修正案,采用起来容易得多。实际上,所需要的是引申第五项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凡私有财产,非有相当补偿,不得收为公有。”
凡是其货币收入刚好赶上通货膨胀的步伐然而被推升到较高纳税等级的人,可以说未经正当手续而被剥夺了财产。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拒绝偿付政府公债的一部分实有价值,就是未经相当补偿而把私有财产收为公有。
有关的修正案可以规定:
美国政府和其他各方之间以美元表示的所有合同,以及列入联邦各种法令中的美元金额,应根据上一年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逐年加以调整。
和稳定货币的修正案一样,这项修正案由于涉及一些技术问题,起草起来也是很困难的。
各种技术细节将不得不由国会来规定,例如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指数反映“一般物价水平”。但是修正案可以阐明基本原则。
到这里,全部工作并未完成——本来我们打算根据人权法案的十项修正案提出十项新的修正案,但我们只提出了七项,还有三项没有完成。而且我们提出的新修正案的措辞,不仅需要研究宪法的法律专家仔细推敲,而且也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们仔细推敲。但是,我们相信,这些修正案至少告诉人们,采用制定新法律的方法解决问题是大有希望的。
结论
人类自由和经济自由这两种思想的携手并进,在美国结出了最丰硕的果实。在我们的头脑里,这些思想仍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我们大家都浸透了这些思想。它们是我们生存的真实依靠。可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偏离了它们。我们忘记了一条基本的真理,即对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权力的集中,无论是集中在政府手里,还是集中在任何其他人手里。我们使自己相信,只要权力的授予是出于高尚的目的,就不会带来损害。
幸运的是,我们醒悟过来了。我们再次认识到一个管制过严的社会的危险,终于懂得好的目标可以被坏的方法所歪曲,懂得了依靠人民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自由地管理他们的生活,乃是使一个伟大社会发挥其全部潜力的最可靠的方法。
同样幸运的是,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仍然可以自由选择走哪条道路——或者是继续沿着我们正在走的道路进一步扩大政府,或者是悬崖勒马,调转方向。
本节内容概述
我们应该采用自我克制的各种法令,以限制我们企图通过政治渠道追求的目标。我们不应该按照其是非曲直考虑每件事情,而应该制定广泛的规章和条例以限制政府的活动范围。
一部成文的——或者与此有关的不成文的——一宪法要发挥效力,它必须在一般公众及其领导人中间得到普遍的舆论支持。
政府对我们的生活进行的许多最有破坏性的管理,并不要政府花许多钱,例如:征收关税,实行物价和工资管制,颁发职业执照,对工业实行管制,颁布保护消费者的法令等。对付所有这些政府管制的最有成效的方法,同样是颁布限制政府权力的一般性法规。
1.国会不得对进口商品或出口商品课以任何进口税或出口税,惟在执行其检查法律上有绝对必要者,不在此限。
2.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以剥夺商品或劳务的卖者对其产品及劳务定价的自由。
3.各州不得制定或施行剥夺合众国公民从事他所选择的工作或职业的权利的任何法律。
4.人们在相互同意的条件下买卖合法的商品和劳务的权利,国会和任何州均不得侵犯之。
对高于个人免征额的全部收入(除真正的职业开支外,不允许有其他扣除),实行一种一刀切的低额税率——低于 20%——会比现有不实用的结构给政府带来更多的收入。纳税人的境况会好一些——因为他们可以省掉因避免所得税而花的费用;经济情况也会好一些——因为税收考虑在资源分配中将起较小的作用。唯一吃亏的人是律师、会计、文职人员以及议员们——他们将不得不从事比填写各种税单、发现税收漏洞并且试图堵塞漏洞等工作更富有成效的活动。
公司所得税也是有很大缺点的。它是一种隐蔽的赋税,公众在所购买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中不知不觉地纳了税。这种赋税对公司所得征两次税——一次是对公司课税,一次是收入分配后对股东课税。它不利于资本投资,从而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它应该被废除。
5.国会有权课征个人所得税,不必问其所得之来源,其收入不必分配于各州,亦不必根据人口普查与统计,只是必须对超过职业与商业开支以及固定数额的个人津贴的一切收入施以同一税率。“个人”一词不包括公司和其他法人。
恢复金币本位制或银币本位制既行不通也不合乎需要,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使货币保持稳定。目前最好的方法,是要求货币当局把货币数量的增长率保持在一个固定的变动范围之内。
6.国会有权批准政府以通货或记帐的形式发行无息债券,如果流通中的美元总额的年增长率不超过5%和不低于3%的话。
也许应该附带这样一条规定,即如果爆发战争,从而使政府停止或延期支付每年应清偿 的债务时,国会参众两院各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或者同样有资格的多数,可以撤销上述要求。
免遭通货膨胀的损害
7.美国政府和其他各方之间以美元表示的所有合同,以及列入联邦各种法令中的美元金额,应根据上一年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逐年加以调整。
和稳定货币的修正案一样,这项修正案由于涉及一些技术问题,起草起来也是很困难的。各种技术细节将不得不由国会来规定,例如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指数反映“一般物价水平”。但是修正案可以阐明基本原则。
我们使自己相信,只要权力的授予是出于高尚的目的,就不会带来损害。
幸运的是,我们醒悟过来了。我们再次认识到一个管制过严的社会的危险,终于懂得好 的目标可以被坏的方法所歪曲,懂得了依靠人民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自由地管理他们的生活,乃是使一个伟大社会发挥其全部潜力的最可靠的方法。
附录
附录一1928年的社会党纲领
以下是1928年社会党纲领中经济政策的条目,括号内的文字说明了实施这些政策的情况。下面列举的包括全部经济条目,但不是每一条都是全文。
1.“将自然资源收归国有,从煤矿和水域开始,特别是博尔德水坝和马斯克尔海滩。”(博尔德水坝和马斯克尔海滩现在都是联邦政府负责的工程。博尔德水坝已改名为胡佛水坝。)
2.“建立一个公有的巨大动力系统,在这个系统下,联邦政府应与州和市政府合作按成本把电力销售给人民。”(已建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3.“将铁路和其他交通运输工具收归国有并对其进行民主管理。”(铁路客运已由全国铁路客运公司全部国有化。某些货运也已由联合铁路公司国有化。联邦电讯委员会控制了电话、电报、无线电和电视通讯。)
4.“在防洪、救洪、造林、灌溉和垦荒方面实施充分的国家计划。”(政府为这些目的开支的经费现在达好几十亿美元。)
5.“扩大所有公共工程,并实施一项长期的公共工程计划,以立即给失业者以政府的救济。”(本世纪三十年代,直接实施这类计划的机构是工程进度管理署和公共工程局;现在这方面的计划多种多样,数不胜数。而由此雇用的人都按小时计工,工资由真正的工会确定。”(戴维斯-培根法案和沃尔什-希利法案要求政府合同的承包人支付“通行的工资”,一般解释为最高的工会工资。)
6.“向州和市政府提供进行公共工程的无息贷款,并采取能减轻广泛困苦的其他措施。”(现在联邦政府给予州和地方政府的补助费每年共达几百亿美元。)
7.“建立一个失业保险系统。”(社会保险系统的一部分起到了这个作用。)
8.“与各城市的劳工联合会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增加政府开办的职业介绍所。”(美国就业局和所属州就业局管理着一个约有二千五百个地方就业办事处的系统。)
9.“建立健康和意外事故保险系统以及养老金和失业保险系统。”(社会保险系统的一部分起到了这个作用。)
10.“缩短工作日”并“保证每个工人每周有不少于两天的假日。”(在这方面,工资和工作时间法已作了规定,要求每周四十小时以外的工作按加班计算工资。)
11.“通过一项全面禁止雇用童工的联邦修正案。”(目前国会还没有通过这样一项修正案;但其要点已体现在各有关法令中了。)
12.为了囚犯及其家属的利益,取消对合同制下的囚犯的残酷剥削,代之以监狱内的工业合作组织和工场。”(目前已部分达到了这一目标。)
13.“增加对高收入阶层征收的赋税,提高公司税和遗产税,所得用于老年补助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险。”(1928年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为25%;1978年为70%;1928年公司税率为12%,1978年为48%;1928年最高的联邦地产税率为20%,1978年为70%。)
14.“对所有用于投机的土地的年租金征税,所得用于政府拨款。”(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一目标,但财产税确实有大幅度增加。)
附录二限制联邦开支宪法修正案草案
联邦修正案起草委员会起草
主席W.C.斯塔莱宾
全国限制税收委员会召集
主席Wm.F.里肯巴克;会长刘易斯·K.尤勒
第一节保护人民,反对政府加给过重的负担,促进健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美国政府的总支出应有限制。
(1)任何财政年度总支出的增长率,不得超过较该财政年度开始前的一个日历年的名义国民生产总产值的增长率。总支出应包括预算和预算外的开支,不包括公债的偿还和紧急开支。
(2)如果某一财政年度开始前的一个日历年的通货膨胀率超过3%,则允许该财政年度总支出除通货膨胀率外的增长幅度应减少四分之一。通货膨胀率应按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之间的差额计量。
第二节当任何一个财政年度美国政府的总收入超过总支出时,其余额应用于减少美国的公债,直到这种债务被消灭。
第三节在总统宣布紧急状态之后,国会可以以两院的三分之二多数表决,授权拨出超过该财政年度限额的特定数量的紧急开支。
第四节对总支出的限制,可以由国会参众两院四分之三多数表决并经多数的州立法部门批准,作特定数量的改变。改变应自批准后的财政年度生效。
第五节在本条款得到批准后的头六年的每一年内,给予州和地方政府的补助费总额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不得小于批准前的三个财政年度的数额。在那以后,如果补助费在总开支中少于那一数额,则应对总支出的限额作相应减少。
第六节美国政府不应直接或间接要求州或地方政府从事额外的或扩大的活动,而不给予必要的补偿。
第七节实施本条款的办法,是由一个或更多个国会议员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提出起诉(其他人没有此项权力)。诉讼应指定美国财政部长为被告。当法院下令实施本条款的规定时,美国财政部长有权过问美国政府的任何单位或机构的支出。法院的指令不应特别指明某项支出照付或削减。遵照法院指令对支出的调整,不得迟于法院指令发出后三个整财政年度。
1979年1月30日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老版本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货币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自由选择》一书是作者在1979年的新著,它本来是一套连续播放十个星期的同名电视节目的讲稿,后经作者对讲稿进行修订补充和润饰而成书。
弗里德曼于1912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市,1932年在拉特格斯大学毕业,1933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48年起任芝加哥大学教授,还担任过剑l桥大学富尔布特讲座讲师、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他还是美国《经济计量学》杂志编辑部的成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员、皮莱林学会会长,被选为1967年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1980年曾来我国访向。
弗里德曼曾在美国资源委员会、美国财政部赋税研究署和美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等政府机构担任经济专家的工作,并且是1969—1971年尼克松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现在又成为参与制订里根总统的经挤政策的有影响的重要人物之一。
弗里德曼出版了许多经济学论著,主要的有:《自由职业收人》(与西蒙·库兹涅茨合著,1946)、《实证经济学论文集》(1953)、《消费函数理论》(1957),《货币稳定方案》(1959)、《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价格理论:一个假定题目》(1962)、《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与安娜·吉·希沃芝合著,1963)、《通货膨胀:原因与后果》(1963)、《国际收支:自由汇率对伸缩汇率》(与罗伯特·弗·鲁萨合著,1967)、《美元与逆差: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与国际收支》(1968)、《货币最优数量和其他(论文集)》(1969)、《货币分析的理论结构》(1971)、《经挤学家的抗议》(1972)、《失业还是通货膨胀:对菲利昔斯曲线的评价》(1975)、《价格理论》(1976)和《自由选择》(1979)。
《自由选择》是由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夫人罗斯·弗里德曼共同署名的合著,他们用通俗的、为广大读者所容易理解的说明方法,阐述弗里德曼多年以来一直鼓吹的贷币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中心内容是揭露国家干预经济的种种弊端,暴露出所谓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括实质上是如何的不自由和不平等.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缩小国家机构,反对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括滥事干预;反对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反对国家的经济调节、社会福利,经济管制和保护贸易措施,反对工会运动,主张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为特色的国内外经济政策,让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整个经济生活,提出所谓回到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政策中去。他们认为,通过市场的作用可以利用人们利己的动机来为广泛的社会目的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包括“负所得税”、“初级和中级教育凭单”等等具体主张。在进行有关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时,他们提出了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处方——即认为经济中存在着所谓自然失业率,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相互交替的关系,用通货膨胀来应付失业或用失业来应付通货膨胀都是无效的,从而他们主张忍受一个时期较高的失业率,而用稳定贷币增长率的办法来医治通货膨胀。
弗里德曼这一著作是以他多年来对美国经济问题和美国货币史的研究为基础的。由于他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起就对当时盛极一时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提出挑战,因而书中在揭露西方世界实行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和国家干预政策的恶果方面有不少经过整理的材料,可供我们在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质,了解西方世界所面临的高赋税、高失业、高通货膨胀率等实际状况时参考。
但必须严肃指出,在《自由选择》一书中,弗里德曼在有的地方把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权和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相提并论,有的地方甚至把我国说成是恐怖国家,这是非常错误的;而弗里德曼的经济理论的基础——现代货币数量论,也是不科学的。
新版本译后记
《自由选择》是由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夫人罗斯·弗里德曼共同署名的合著,他们用通俗的、为广大读者所容易理解的说明方法,阐述弗里德曼多年以来一直鼓吹的贷币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中心内容是揭露国家干预经济的种种弊端,暴露出所谓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括实质上是如何的不自由和不平等.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缩小国家机构,反对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括滥事干预;反对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反对国家的经济调节、社会福利,经济管制和保护贸易措施,反对工会运动,主张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为特色的国内外经济政策,让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整个经济生活,提出所谓回到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政策中去。他们认为,通过市场的作用可以利用人们利己的动机来为广泛的社会目的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包括“负所得税”、“初级和中级教育凭单”等等具体主张。在进行有关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时,他们提出了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处方——即认为经济中存在着所谓自然失业率,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相互交替的关系,用通货膨胀来应付失业或用失业来应付通货膨胀都是无效的,从而他们主张忍受一个时期较高的失业率,而用稳定贷币增长率的办法来医治通货膨胀。
【按:老版本最后的出版说明体现出十足的求生欲,据译者本人在豆瓣上的吐槽出版社删改太过严重。】
资本主义与自由
- 简介
- 绪论
- 第一章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
- 第二章自由社会中政府的作用
- 第三章货币的控制
- 第四章国际金融和贸易安排
- 第五章财政政策
- 第六章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作用
- 第七章资本主义和歧视
- 第八章垄断以及企业和劳工的社会责任
- 第九章职业执照
- 第十章收入的分配
- 第十一章社会的福利措施
- 第十二章贫穷的减轻
- 第十三章结论
简介
英文名:Capitalism and Freedom
作者:Milton Friedman
本文来源版本:商务印书馆2004-4出版
该版本翻译极为差劲,好多内容缺失,此外“涉及到”的频繁出现让我内心犹有一万只羊驼穿过~
[在线阅读英文版pdf](https://rosefinch-midsummer.github.io/Books/file/Economics/Capitalism and Freedom.pdf)
作者区分了市场和政府各自的作用,给我带来不少的启发,能更好地理解和拓展《自由选择》中的内容!
政府的作用主要为如下内容:
总之,通过自愿交换而组织的经济活动系以下列假设条件为前提:通过政府我们提供了法律和秩序的维护,以使防止一人受到另一人的强制行为,提供了自愿参与的合同的强制执行,提供了财产权的意义的定义,提供了对这种权利解释和强制执行的办法以及提供了货币机构。
绪论
在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中被引用得很多的一句话是“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关于这句话的论争集中于它的起源而不是它的内容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的一个显著的特征。这句话在整个句子中的两个部分中没有一个能正确地表示合乎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人的理想的公民和它政府之间的关系。家长主义的“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这个观点和自由人对他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信念不相一致。带有组织性的,“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则为仆人或信徒。对自由人而言,国家是组成它的个人的集体,而不是超越在他们之上的东西。他对共同继承下来的事物感到自豪并且对共同的传统表示忠顺。但他把政府看作为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既不是一个赐惠和送礼的人,也不是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
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他会问的是:“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以便尽到我们个人的责任,以便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伴随这个问题他会提出另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使我们建立的政府不至成为一个会毁灭我们为之而建立的保护真正自由的无法控制的怪物呢?自由是一个稀有和脆弱的被培育出来的东西。我们的头脑告诉我们而历史又能加以证实: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的集中。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政府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这一工具我们可以行使我们的自由;然而,由于权力集中在当权者的手中,它也是自由的威胁。即使使用这权力的人们开始是出于良好的动机,即使他们没有被他们使用的权力所腐蚀,权力将吸引同时又形成不同类型的人。
我们怎么能从政府的有利之处取得好处而同时又能回避对自由的威胁呢?在我们宪法中体现的两大原则给与了迄今能保护我们自由的答案,虽然这些原则被宣称为根本的方针而在实际上它们屡次受到破坏。
首先,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具有限度。它的主要作用必须是保护我们的自由以免受到来自大门外的敌人以及来自我们同胞们的侵犯:保护法律和秩序,保证私人契约的履行,扶植竞争市场。在这些主要作用以外,政府有时可以让我们共同完成比我们各自单独地去做时具有较少困难和费用的事情。然而,任何这样使用政府的方式是充满着危险的。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避免以这种方式来使用政府。但是在我们这样做以前,必须具备由此而造成的明确和巨大的有利之处作为条件。通过在经济和其他活动中主要地依靠自愿合作和私人企业,我们能够保证私有部门对政府部门的限制以及有效地保证言论、宗教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个大原则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当政府行使权力时,在县的范围内行使比在州的范围内要好,在州的范围内要比在全国的范围要好。假使我不喜欢我当地城镇所做的事情,哪伯是污水处理,或区域划分,或学校设施,那末,我能迁移去另一个城镇。
虽然很少人会实际采取这一步骤,仅仅是这种可能性就能起着限制权力的作用。假使我不喜欢我居住的那个州所做的事情,那末,我能迁移去另一个州。假使我不喜欢华盛顿实施的事项,那末,在这个各国严格执行自主权的世界里,我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当然,成立联邦政府的不利之处对许多主张成立的人来说恰恰是权力集中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地方。他们相信这会使他们更有效地——象他们所看到的那样——以公众的利益来进行立法,不管它是把收入从富人转移给穷人,还是从私人的用途转到政府的用途。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正确的。但这个事物有正反两面,做有益的事的权力也是做有害的事的权力。今天控制权力的那些人不可能明天也如此,而更重要的是:一个人认为是有益的东西,另一个人可能认为是有害的。正象进行鼓动来一般扩大政府范围的悲剧一样,鼓动权力集中的最大悲剧是它主要是由那些首先会对其后果懊悔的有善良意愿的人所领导。
保存自由是限制和分散政府权力的保护性原因。但还有一个建设性的原因。不管是建筑还是绘画,科学还是文学,工业还是农业,文明的巨大进展从没有来自集权的政府。
哥伦布并不是由于响应议会大多数的指令才出发去找寻通往中国的道路,虽然他的部分资金来自具有绝对权威的王朝。牛顿和莱布尼茨,爱因斯坦和博尔,莎士比亚、米尔顿和帕斯特纳克,惠特尼、麦考密克、爱迪生和福特,简·亚当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和艾伯特·施韦特,这些在人类知识和理解方面,在文学方面,在技术可能性方面,或在减轻人类痛苦方面开拓新领域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出自响应政府的指令。他们的成就是个人天才的产物,是强烈坚持少数观点的产物,是允许多样化和差异的一种社会风气的产物。政府永远做不到象个人行动那样的多样化和差异的行动。在任何时候,通过对房屋或营养或衣着的统一的标准,政府无疑地可以改进许多人的生活水平,而通过对学校教育、公路建筑式卫生设备设置统一的标准,中央政府能无疑地改进很多地区.甚至平均说来所有地区的工作水平。但是在上述过程中,政府会用停滞代替进步,它会以统一的平庸状态来代替使明天的后进超过今天的中游的那个试验所必需的多样性。
这本书讨论了这些大问题中的一部分。它的主要论点为竞争的资本主义——即通过在自由市场上发生作用的私有企业来执行我们的部分经济活动——是一个经济自由的制度,并且是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本书的次耍的论点是:政府在致力于自由和主要依赖市场组织经济活动的社会中所应起的作用。
头两章按照原则而不是按照具体的应用在抽象的水平上论述这些问题。后面几章则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各种特殊的问题。
一个抽象的论述可以被设想为是完整和彻底的,虽然这种设想在头两章中肯定是远未实现。这些原则的应用甚至在设想中也不可能是彻底的。每天都产生新的问题和新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国家的作用的具体形式永远不能在一次中加以彻底说明而无需再加以补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经常结合当前的问题再次审查被我们遵崇为不变的原则的现实意义。其中的副产品不可避免地是对这些原则的再次考验以及加深我们对原则的理解。
对这本书所阐述的政治和经济观点加上一个名称是非常有用的。正确和适当的名称是自由主义。不幸地,“作为一种最高的但未必是故意的颂扬,私人企业制度的敌人曾认为占用这一制度的名称是有利的,”因此,在美国,自由主义逐渐有着和它在十九世纪以及和在今天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很不相同的意义。
当它在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早期被发展出来的时候,以自由主义名义进行的思想运动把自由强调为最后目标,而把个人强调为社会的最后实体。在国内,它支持自由放任主义,把它当作为减少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从而扩大个人作用的一个手段。在国外,它支持自由贸易,把它当作为世界各国和平地和民主地联系在一起的手段。在政治事务中,它支持代议政体和议会制度的发展,减少国家的无上权力和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
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尤其是美国在1930年以后,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中,自由主义这个术语逐渐和很不相同的主张联系在一起。逐渐和它相联系的是:主要依赖于国家,而不是依赖于私人自愿安排来达到目标被认为是较好的办法。它的主旨成为福利和平等而不是自由。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扩大自由认为是改进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的方法。
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和平等看作为自由的必要条件或者是它的替代物。以福利和平等的名义,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逐渐赞成恰恰是古典的自由主义所反对的国家干涉和家长主义政策的再度出现。把时钟拨回到十七世纪重商主义的行动中,上述自由主义者喜欢把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谴责为反动派。
附着在自由主义术语上的意义的变化在经济事务中比在政治事务中更为显著。二十世纪自由主义者,象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一样,赞成议会体制、代议政体、公民权利等等。然而,甚至在政治事务中。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差异。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由于酷爱自由,惧怕不管在政府或私人手中的集权,所以他赞成政治上的分权。由于致力于行动并且相信只要在表面上由选民控制的政府手中权力的仁慈的作用,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赞成中央集权的政府。关于权力应该放在州一级还是城市一级,放在联邦一级还是州一级。放在世界范围的组织还是国家政府中,他会提供任何解除疑虑的答案。
由于自由主义这一名词的滥用,以往属于那个名词的观点现在常常被称为保守主义。
但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在这一名词的语义来源方面以及在赞成社会制度较大改革的政治方面都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因此,他的现代继承者肯定也是如此。我们不希望保留干涉我们自由那么多的国家的干涉,虽然我们当然希望保留那些改进自由的东西。此外,保守主义这个术语实际上逐渐包括如此广泛的一系列的观点,包括相互之间的矛盾如此之多的观点,以致于我们无疑地将看到复合名称的增长,例如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贵族政治——保守主义。
部分地由于我不愿意向赞成毁灭自由的措施的人放弃这个名词,部分地由于我不能找到更好的代替物,我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是以其原有的意义来使用自由主义这个名词——作为有关自由的人的学说。
第一章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
人们普遍相信政治和经济是可以分开的,并且基本上是互不相关的;相信个人自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物质福利是一个经济问题,并且相信任何政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经济安排结合在一起。当前这种思想的主要表现是很多人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些人强烈谴责苏联“集权社会主义”强加于个人自由的种种限制的严重程度,并认为一个国家有可能采用苏联经济安排的主要特征,然而又能够通过政治安排来保证个人自由。这一章的论点是:这种观点是一种错觉;在政治和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和经济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特别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在保证个人自由的意义上不可能是民主的。
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
在经济自由的上述两种作用中,需要特别强调第一种作用,因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于把这方面的自由放在重要地位具有一种强烈的偏见。他们倾向于蔑视那些被他们看作为生活的物质方面的东西,并且倾向于把他们自己追求的被认为具有较高价值的东西看得不可比拟的重要,从而值得特别加以重视。然而对我们国家的极大多数公民来说,如果不是对知识分子来说的话,作为政治自由的一个手段,经济自由的直接重要性的意义至少可以和经济自由的间接重要性相提并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外汇控制,英国公民不准去美国度假;在这件事情中,英国公民所被剥夺掉的基本自由正和美国公民由于政治观点而不准去苏联度假一样。在外表上,一个是对自由的经济限制,而另一个是对自由的政治限制;然而两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法律迫使美国公民使用大约其收入的10%来购买政府经营的某种特殊退休合同,在其中,美国公民被剥夺掉其个人自由的相应部分。这种剥夺的被感觉到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以及它和被大家认为是“个人的”或“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宗教自由有多么密切的相似之处可以在有关亚米西教派的一群农民的一个事件里找到戏剧性的表现。根据信仰的原则,这群人认为强制性的联邦的老年退休方案侵犯了他们的个人自由,从而拒绝付税或享受其利益,结果,为了满足社会保险的要求,他们的一些牲畜被拍卖掉。确实,把强制性的老年的退休保险看作为剥夺自由的公民们可能不多,但对信仰自由的人是从来不计算人数多寡的。
在不同州的法律规定下,一个美国公民没有自由来选择自己的职业,除非他获得从事该职业的执照。这样的一个公民同样地是在被剥夺其个人自由的实质的一部分。同样情况也存在于那些愿意用自己的一些货物向瑞士人,譬如说,去换取一只表但却由于外贸限额而不能这样做的人。同样情况也适用于那些为了以低于制造商所订立的价格来出售阿尔加矿泉水,并且按照所谓“公平交易”法而被投入监狱的加里福尼亚州的人。同样情况也适用于那些不能生产他自己所愿意生产的数量的小麦的农民,如此等等。显然,经济自由本身以及它所牵涉到的事物构成整个自由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部分。
由于经济安排对权力的集中和分散权力所具有的影响,作为获得政治自由的一个手段,经济安排是很重要的。直接提供经济自由的那种经济组织,即竞争性资本主义,也促进了政治自由,因为它能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分开,因之而使一种权力抵消掉另一种。
关于政治自由和自由市场之间的关系,历史的例证是和上述一致的。我找不到任何例证来表明:人类社会中曾经存在着大量政治自由而又没有使用类似自由市场的东西来组织它的大部分的经济活动。
因为我们生活于一个基本上是自由的社会里,我们倾向于忘掉象政治自由这样的东西在世界上的存在,从时间和地区来看都是很有限的。人类典型的情况是:专制、奴役和痛苦。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西方世界是历史发展总趋势的突出的例外。以这个事例而论,政治自由显然是随着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到来的。希腊的黄金时代和罗马时代的早期政治自由也是如此。
历史仅仅表明: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显然这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法西斯的意大利,法西斯的西班牙,过去七十年间不同时期的德国,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中的沙皇俄国——这些都不可能被称为是政治上自由的社会。然而,在以上各个社会中,私有企业是经济结构的主要形式。因此,明显地存在着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安排而同时又没有自由的政治安排的可能性。
甚至在那些社会中,一般公民要比现代极权主义国家,如经济极权和政治极权结合在一起的苏联或纳粹德国的公民具有大量更多的自由。甚至于在沙皇时代的俄国,某些公民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不经政治领导当局的批准来调换工作,因为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存在给国家的集中权力提供了某些限制。
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但决不是一个方面导致另一方面。十九世纪初期,边沁和哲学的激进主义者倾向于把政治自由看作为经济自由的一种手段。他们相信:群众受到强加于他们身上的种种限制的束缚,并且相信:假使政治改革给与大部分人民以选举权,他们会做对他们有益的事,即选择自由放任。回想起来,我们不能说他们是错误的。很大程度的政治改良和趋向大量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改革伴随在一起。随着这种经济安排的变化,群众的福利大幅度增加。
在边沁自由放任主义于十九世纪的英国取得胜利以后,接着到来的反作用即是对经济事务日益增长地进行干预。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英国和其他各地大大加速了这个集体主义的倾向。福利而不是自由成了民主国家的决定性的主张。由于认识到对个人主义的内在的威胁,哲学的激进主义者的思想上的继承人——这里随意提到几个,如迪赛、米塞斯、哈耶克和西蒙斯——他们担心:继续集中控制经济活动会造成《通向奴役的道路》,正如哈耶克对这个过程所作的透彻分析的名称所示,他们所强调的是把经济自由作为政治自由的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事实显示了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另一种不同的关系。集体经济计划确实干扰了个人自由。然而,至少在某些国家中,结果并不是压制了自由,而是把经济政策倒转了过来。英国再一次提供了最显著的例子。或许转折点是“协议控制”法令。尽管存在着疑虑,工党认为:该法是为了执行它的经济政策所必要的。如果彻底地强制执行,这个法令肯定会引起对个人职业的集中安排。这和个人自由相冲突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于只能在很少量的事例中加以实施,随后在很短时期中将该法撤消。该法规的撤消促使了经济政策决定性的改变,其特点为:对集中“计划”和“方案”依靠的减少,对种种控制的取消,和对私营市场的日益重视。在大多数其他民主国家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政策的改变。
这些政策变更的大致原因是中央计划的成就不大,或完全没有达到既定的目标。然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次失败本身应归因于中央计划牵涉到的政治问题,和归因于不愿意把政策执行到应有的程度。因为,这样做需要残暴地践踏宝贵的个人权利。这种改变很可能仅仅代表对这个世纪集体主义倾向的一个暂时的间歇。即使如此,它说明了政治自由和经济安排之间的密切关系。
仅凭历史的例证本身从来是没有说服力的。或许自由的扩大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市场机制发展同时发生仅仅是一种巧合。为什么它们之间会有联系呢?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逻辑上的联系是什么呢?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将首先把市场看作为自由的直接的组成部分,然后考察市场安排和政治自由之间的间接联系。这个讨论的副产品将是为自由社会的理想的经济安排提供一个轮廓。
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把个人自由,也许或者是家庭自由作为我们鉴定社会安排的最终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生活目标的自由牵涉到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对住在荒岛上的鲁滨逊(不算进他的仆人礼拜五)根本不存在任何意义。住在荒岛上的鲁滨逊是受到“约束”的。他具有有限的“权力”,他只有少量的选择的余地。但是,在与我们的论述有关的意义上,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同样,在一个社会中自由是与个人如何使用他们的自由是无关的。它不是一个包括一切的伦理问题。确实,自由主义者的主要目的是把伦理问题让每个人自己来加以处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在一个自由社会中的个人所面临的那些问题——即他应该如何使用他的自由。因此,自由主义者将强调两种意义的自由——一种是和人们之间关系有关的意义的自由,它是自由主义者把自由当作为第一个考虑因素的出发点;另一种意义的自由关系到个人如何使用他的自由,它属于个人伦理和哲学的范畴。
自由主义者把人当作为不完善的实体。他把社会组织问题看作为消极地防止“坏人”做坏事的程度等于他把同一问题看作为能使“好人”做好事的程度。当然“坏人”和“好人”可能是同一的一个人,取决于谁来鉴定他们。
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协调许多人的经济活动。甚至在相当落后的社会中,广泛的劳动分工和职能专业化都是为了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而必需具备的条件。在先进的社会中,为了能充分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所提供的机会,需要进行协调的规模更加巨大。实际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卷入于彼此供应日常的面包的活动,更不用说供应每年的汽车了。信仰自由的人的战斗任务是要把这个普遍的相互依存和个人自由结合起来。
从基本上说,仅有两种方法来协调千百万人的经济活动。一个方法是包括使用强制手段的中央指挥——军队和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方法。另一个是个人自愿的结合——市场的方法。
通过自愿的结合进行协调的可能性来自一个基本的——然而经常被否定的——命题,即:进行经济交易的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利,只要交易双方是自愿的而且是不带欺骗性的。
因此,交换可以不用强制手段而带来协调。通过自愿交换所组成的社会的一个发生作用的模型是一个自由的私有企业交换经济——即:我们一向称之为竞争的资本主义。
以它的最简单形式而论,这种社会包含许多独立的家庭——好象是许多不同的鲁滨逊。每一个家庭利用它控制的资源来生产物品和劳务用以和其他家庭生产的物品和劳务进行交换,并按照双方相互能接受的条件来进行。因此,它可以间接地通过为别人生产物品和劳务来满足他的需要,而不是直接地生产自己立即能使用的物品。当然,采用这种间接方式的动机是通过劳动分工和职能专业化而成为可能的产品增加。由于每个家庭总是可以选择直接为自己生产的办法,它就不需要进行交换,除非能有利可图。如果从交换中得不到好处,它就不会这样做。所以,双方均能得到好处,交换才会发生。这样,在没有强制手段的情况下也可以达到合作目的的协作。
假使最终的生产单位是家庭,职能专业化和分工不会有很大效果。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已经把事态推到很远的程度。我们采用了企业的形式;它是个人作为劳务供应者和物品购买者之间的媒介。同样,职能专业化和分工不可能具有很大效果,假使我们不得不继续依赖于物物交换的话。结果,我们采用了货币作为方便交换的手段和作为使买和卖的行动成为两部分的手段。
尽管在我们实际的经济中企业和货币有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它们会引出大量而复杂的问题,达成协调的市场方法的主要特征已经在既没有企业又没有货币的简单交换经济中充分地显示出来。在简单模型的经济中,和在复杂的具有企业和货币交换的经济中一样,合作完全是个人的和自愿的,其前提条件为:(a)企业是私有的,从而,签订合同双方最终还是个人;(b)个人确有自由来参与或不参与任何具体的交换,从而每件交易完全是自愿的。
一般地来说这些前提条件要比详细地把它们说出来,或者准确地说明最有利于维持这些条件的制度安排是什么要容易得多。的确,极大部分技术性的经济文献恰恰是论述这些问题的。基本要求之点是维持法律和秩序以便使一人在体力上不受另一个人的强制,以便强制执行自愿缔结的契约,从而使“私人”这一名词具有实质性的内容。除此以外,或许最棘手的问题会来自垄断——它在具体的交换中,不让个人进行选择,因而阻碍了有效的自由——以及来自“邻近的影响”——即:对不可能向之索价和赔偿的第三方的影响。这些问题将在下一章更详细地加以讨论。
只要能维持有效的交换自由,经济活动的市场组织的主要特征是:在大多数的活动中,它能避免一人对另一人的干扰。消费者可以免于受到销售者的强制性的压迫,因为有其他的销售者,他可以与其他的销售者进行交易。销售者也可以免于消费者的强制性的压迫,因为他能出售给其他的消费者。雇员可以免受雇主的强制性的压迫,因为他可以为其他雇主工作,等等。同时,市场按照与具体的个人无关的方式来这样做,并不存在着一个集中的权力机构。
的确,反对自由经济的主要来源就是由于它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它给人们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特殊集团认为他们应该需要的东西。在反对自由市场制度的各种论点中,最基本之点是缺乏对自由本身的信任。
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相反地,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市场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通过政治渠道的行动的主要特征是: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趋于要求和强制执行对命令的服从。另一方面,市场的巨大优越性是它允许广泛的多样性的存在。以政治术语来说,它是一种比例代表制的体制。好象是每个人能对他所需要的领带颜色进行投票并且得到这种领带,而并不需要观察大多数人所需要的领带颜色,从而,如果他属于少数派的话,必须顺从大多数的意见。
当我们说市场提供经济自由时,我们所指的正是市场的这种特征。但这种特征所具有的含义远远超过狭窄的经济的范围。政治自由意味着一个人不受其他人的强制性的压制。对自由的基本威胁是强制性的权力,不论这种权力是存在于君主、独裁者、寡头统治者或暂时的多数派。保持自由要求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排除这种集中的权力和分散任何不能排除掉的权力——即:相互牵制和平衡的制度。通过使经济活动组织摆脱政治当局的控制,市场便排除了这种强制性的权力的泉源。它使经济力量来牵制政治力量,而不是加强政治力量。
经济力量能够广泛地被分散开来。并没有一个守恒规律来规定:新的经济力量的中心的增长必须以牺牲现有的中心作为代价。另一方面,政治力量的分散则较为困难。可能有大量的小而独立的政府。但是要在单一的大政府里来保持很多的势均力敌的政治力量中心要比在一个单一的大的经济制度里保持很多的经济力量中心难得多。在一个大的经济制度里,可能有许多百万富翁。但是,能否有一个真正杰出的领袖,把一国的国民的热情及精力集中起来呢?假使中央政府的权力增加,增加的权力很可能来自牺牲地方政府的权力。似乎存在着类似有待于分配的权力固定不变那样的情况。因此,假使经济力量加入政治力量,权力的集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假使经济力量保持在和政治力量分开的人的手中,那末,它可用作为政治力量的牵制物和抗衡物。
这个抽象的论点的主旨或许能够通过事例加以最好的说明。我们首先考虑一个设想的事例,以便表明所涉及到的原则;然后再考虑一些从最近的经验中得来的事例,以便说明市场如何发生作用来保持政治自由。
自由社会的一个特征肯定是个人能公开主张和宣传急剧地改变社会结构的自由——只要主张和宣传被局限于说服,而不包括暴力或其他强制的形式。人们能公开地主张和宣传社会主义并且为社会主义而出力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自由。同样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自由应该使人们能自由地进行采用资本主义的主张和宣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怎么能保护主张资本主义自由的人呢?
为了使人们能有任何的主张,人们首先必须要能够谋生。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已经形成了问题,因为一切工作的机会都在政治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对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来说,允许它的雇员采用和官方思想直接相违背的政策,要求采取自我克制的行动,其中的困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联邦雇员之间所谓“安全”问题而在美国历史上突出地表现出来。
但是,我们假设这种自我克制的行动是可以实行的。为了使赞成资本主义的主张具有任何现实意义,赞成者必须有可能对他们的事业提供资金——来举行公共集会,印刷小册子,购买广播时间,出版报纸和杂志,以及其他等等。他们如何能筹集这笔资金呢?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可能和或许有人具有很大的收入,甚至有一大笔以政府公债以及类似形式存放的资金;但是,这些人必然是高级政府官员。可能设想有这么一个低级的社会主义官员,虽然公开主张资本主义,但还能保留着他的工作。然而,想象社会主义上层高级官员来提供资金支持这种“颠覆活动”是难于令人置信的。
资金的唯一来源会是从大量的低级官员那里筹集到少量的款项。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答案。要想使用这种来源,许多人应该已经受到宣传的说服,而我们的整个问题是如何发动达到这个目的的运动,并为这个运动筹集资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激进运动从未以这种方法来筹划资金。这种运动的典型情况是由几个被说服了的富人所支持——这儿提几个目前有名气者的名字,加弗雷德里克·范德比尔特·菲尔德,或安尼塔·麦考密克·布莱恩,或科利斯·拉蒙特,或在更远以前的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是很少为人注意到的财富的不平等保存政治自由的作用——即资助人的作用。
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只需要说服几个富有的人提供资金来实现任何想法;不管想法是多么古怪,都是如此。这样的人大量存在,具有独立见解的人的支持也大量存在。的确,甚至于没有必要去说服持有资金的人们或金融机构,使他们相信有待于宣传的思想的完善性质。只需要向他们说明:在财政上,宣传是能够成功的;报纸、杂志或书刊或其他活动是有利可图的。例如,竞争的出版商不能出版仅仅为他个人所同意的著作,他的关键问题是销售量是否大到使他的投资能得到满意的报酬。
市场以这种方式打破了恶性循环,使得不需要首先说服人们而最后从他们那里筹集少量冒风险的资金成为可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这种可能的只有一个具有无上权力的国家。
让我们扩展一下我们的想象力来设想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而该政府系由渴望保持自由的人们所组成。这个政府能否提供资金?或许可能,但在实际上很难做到。它可以建立一个局来贴补颠覆性的宣传。但是,它如何来选择被贴补的人呢?假使它把资金给与所有要求支持的人,那末,它不久会发现自己已经没有资金可给,因为社会主义不能废除一条基本的经济规律,即:足够高的价格会导致出大量的供给。只要使激进事业的主张得到足够的报酬,那末,提供这种主张的人会是无限的。
此外,宣传不受欢迎的主张的自由并不是说这种宣传是不需要代价的。相反,假使激进改革的主张不需要代价,更不用说去贴补它们,那末,就不可能存在着稳定的社会。人们为了宣传自己所深信的主张而作出牺牲,这是完全适宜的。的确,重要的是要让那些愿意自我牺牲的人保持自由,因为不然的话,自由会蜕化成为放肆和无责任感。问题的实质是:应该容忍不受欢迎的主张的宣传,并且不要使宣传的代价高到无法支付的程度。
但是我们的话还没有说完。在一个有自由市场的社会里,有了资金便有了一切。纸张供应者愿意销售给《工人日报》和愿意销售给《华尔街日报》的程度是一样的。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仅仅有资金是不够的。我们设想的那位资本主义支持者必须说服政府的造纸工厂把纸销售给他,说服政府的印刷厂印刷他的小册子,政府的邮电局把小册子分送给人们,政府的有关机构租给他一个礼堂以便进行演讲,如此等等。
或许有人能以某种办法克服这些困难,从而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保持自由。我们不能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要建立有效的保护不同意见的机构显然具有非常大的真正困难。据我所知,没有一个赞成社会主义而又赞成自由的人曾经真正地正视这个问题,或者甚至实事求是地开始发展出在社会主义中容许自由的制度上的安排。与此相对照,一个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助长自由是很清楚的。
这些抽象原则的一个显著的实际事例是温斯顿·丘吉尔的经历。从1933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丘吉尔不被准许在英国电台广播中讲话。英国广播电台当然是英国广播公司所经营的一个政府的垄断机构。这里是一个英国的领导人物、议会议员、前内阁部长,正在千方百计地想方设法说服他的同胞们采取步骤来避免希特勒德国的威胁。但他没有被批准在电台广播中和英国人民讲话,因为英国广播公司是政府的一个垄断机构,而他的意见“具有很大的争论性质”。
另一个显著的事例是1959年1月26日《时代》杂志所报导的和“黑名单的消失”有关的事情。《时代》杂志的报导如此说:
奥斯卡奖的获奖仪式是好莱坞的尊严的最高峰,但在两年前,其尊严受到了损害。当宣布罗伯特·里奇——这人是《勇敢的人》一片的剧作者时,没有人出来接奖。罗伯特·里奇是一个假名。它掩盖了1947年以来被企业怀疑是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同路人而列入黑名单内的约150名作者之一。这个事件特别令人难堪,因为,电影评议会禁止任何共产党人或引用第五修正案的人参与奥斯卡奖的竞争。上星期,共产党法则和里奇身份的秘密都突然得到正式的答案。
里奇原来就是多尔顿·特朗博《约翰尼得到了他的枪》的作者。他是1947年电影业有关共产主义审讯会拒绝作证的“好莱坞十人”作家中的一个。曾断然地坚持罗伯特·里奇是《西班牙的一个有胡子的小伙子》的制片商的弗兰克·金说:“对我们的股东来说,我们有义务购买我们能买到的最好的剧本。特朗博给我们带来了《勇敢的人》,我们便把它买下来”……。
实际上,这是好莱坞黑名单的正式终结。对那些受到禁止的作者而言,非正式的终结早已到来。据报导,在目前好莱坞影片中,至少15%的剧本是由黑名单上的成员写的。制片商金说,“好莱坞的鬼作家要比任何地方都多。城中的每一家公司都用黑名单上人们的作品。我们只是第一个证实了大家知道的事情。”
人们可以象我一样相信,共产主义会摧毁我们所有的自由。我们可以尽量坚定和强烈地去反对它,然而同时,我们也相信: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一个人不能由于相信或试图促进共产主义便因之而不能自愿地和其他人达成相互有利的协议。他的自由包括促进共产主义的自由。当然,自由也包括在这些情况下别人不和他来往的自由。好莱坞的黑名单是摧毁自由的非自由的行为,因为,它是一种使用强制手段来阻止自愿交换的暗中勾结的安排。黑名单没有起作用,恰恰因为市场使人们为了保持黑名单而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商业所强调的这个事实,即:经营企业的人们有一个尽可能多赚钱的动机,保护了列入黑名单那些人的自由,因为,这一事实向这些人提供了另一形式的就业机会,并且向人们提供在用这些人的动机。
假使好莱坞和电影业是政府的企业单位,或者仅使在英国这是一个英国广播公司雇用的问题,那就难以相信“好莱坞十人”或类似他们的人会找到工作。同样,在那些情况下,也难以相信强烈赞成个人主义和私营企业的人——或者,那些强烈赞成与现状不同的观点的人——会有可能找到工作。
另一个市场在保存政治自由上的作用的事例通过我们的麦克锡主义的经验中表现出来。姑且完全不谈其中所涉及的实质问题以及其中的指控是否有道理,个人特别是政府的雇员具有什么保护性的措施来避免不负责任的控告和调查所要求他们进行的违背良心的揭发呢?引用第五修正案肯定会是一个空洞的嘲弄行为,因为,它并不提供政府以外的其他就业途径。
他们的最基本的保护措施便是人们能够在其中谋生的私人市场经济的存在。在这里,保护也并不是绝对的。很多有可能雇用人的私方雇主,不论正确与否,往往不喜欢在用公开受到怀疑的人。雇用这些人所支付的代价很可能要小于这些宣传不受欢迎的主张的人为之而支付的代价。但是,重要的问题是:代价是有限的,而且不象政府工作是唯一可能的情况的代价那样大到无法支付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所涉及到的人的极大部分,显然进入了竞争性很强的经济部门——小商业、贸易、农业——在那些部门,市场最接近于理想的自由市场。买面包的人谁也不知道做成面包的面粉是由一个共产主义者还是一个共和党员种植的,或是由一个立宪主义者还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种植的。或者就此而言,是由一个黑人还是一个白人种植的。这说明了一个不以个人为转移的市场如何把经济活动与政治观点分开,从而,保护人们使他们经济活动免于受到由于和他们的生产力无关的理由而受到的歧视——不管这些理由和他们的观点还是和他们的肤色具有联系。
正如这个例子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在我们社会中,对保存和加强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关系最大的人群是那些最容易成为大多数人不信任和敌视对象的少数集团——仅就其中最显著的而论,便是黑人、犹太人、外国出生的人。然而,奇怪的是:自由市场的敌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这些集团里所占有的比例大于这些集团在人口中所占有的比例。他们没有认识到市场的存在保护了他们,使他们部分地避免他们的同胞的歧视态度,而错误地把未能避免的歧视归因于市场。
第二章自由社会中政府的作用
对集权社会普遍的不满意见是他们用目的来为手段辩护。从字面上看,这种不满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假使目的不能为手段辩护,那什么能为手段辩护呢?但这个简单的回答并没有解决这个不满的问题,而只是说明:这个不满表达得不够完善。否定目前为手段辩护是间接地主张所谈论的目的并不是最后的目的,而最后的目的本身是使用适当的手段。不管是否为一个理想的目的,任何仅仅通过坏的手段而能达到的目的,必须让位于使用合适的手段而达到的较基本的目的。
对一个自由主义者而言,合适的手段是自由讨论和自愿合作。这也就意味着:任何强制的形式都是不合适的。理想的情况是:在自由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具有责任心的个人之间取得一致的意见。这是前一章所强调的自由目的的另一个表示方法。
从这个观点来看,正象早已说过的那样,市场的作用在于在没有顺从的情况下可以取得一致的意见。它实际上是一种有效的比例代表制。另一方面,直接通过政治渠道的行动特征是:它趋于需要或强制执行相当大的程度的顺从。典型的争论问题必须决定“是”还是“否”,最多也不过能提供非常有限的不同选择。甚至使用比例代表制这一直接政治形式也不会改变上述结论。事实上,能够代表的各个不同集体的个数是非常有限的,而和市场所能代表的不同集体的个数相比,则有限的程度更为突出。更为重要的事实是:最后的结果一般会是制定对所有的集体都适用的法律,而不是对每一个代表的“党”制定一个特殊的法律。这事实意味着:比例代表制的政治形式,远不能实现在没有顺从的条件下的意见一致;它具有无效和片面的趋向。因此,它的作用是破坏没有顺从的条件下的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
显然存在着某些使有效的比例代表制成为不可能的事项。我不能获得我愿意要的国防费用数量,而你也不能获得你要的不同的数量。关于这种不可分割的事项,我们可以讨论、争论和进行投票。但一经决定,我们必须顺从。正是由于这些不可分割的事项的存在——保护个人和国家免于受到强制性的行动显然是最基本的问题——才使我们不全然依靠通过市场的个人的行动。假使我们为这些不可分割的项目而使用我们的一些资源,我们必须使用政治渠道来调和我们之间的差距。
虽然使用政治渠道是不可避免的,它趋向于削弱一个稳定的社会所必需有的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假使共同行动的协议只限于有限范围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会同意的问题,那末,削弱的程度会是最少的。对取得协议的问题范围的每一次扩展会进一步绷紧把社会连在一起的脆弱的线。假使事情发展到触及到人们感情深处而又有不同意见的问题,那很可能要瓦解这个社会。有关基本价值的根本性的差异如果不是永远不可能,那也很少能用投票的方法得以解决。它们在最后只能通过斗争而得以决定,并不是得以解决。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和内战是这种判断的流血的证明。
广泛地使用市场可以减少社会结构的紧张程度,因为,它使它所进行的任何活动都没有顺从的必要。市场所涉及的范围愈广,纯然需要政治解决的问题愈少,从而需要达成协议的问题愈少。反过来说,需要达成协议的问题愈少,在维持一个自由社会的条件下取得协议的可能性愈大。
意见一致当然是一种理想。实际上,我们花不起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在每一问题上达到完全的一致。我们不得不降低标准。这样,我们因之而以某种形式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作为权宜之计。我们愿意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的程度以及有效的多数达到何种程度,这取决于所涉及的问题的严重性质。这一事实很清楚地表明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是个权宜之计,而本身不是一个基本原则。假使事情很少有重要性,而少数人遭受否决又不会引起强烈反应,那末,仅过半数就可以通过。另一方面,假使少数人对牵涉到的问题具有强烈的感觉,那末,甚至明确的多数票也无济于事。在我们中间很少有人愿意,譬如说,把言论自由问题按照明确的多数票来决定。我们的法律制度中充满了不同问题要求不同程度的多数的事例。那些包含在宪法里的问题是极端的情况。这些是重要的原则问题,以致我们仅愿意对权宜之计作出最小的让步。在最初接受这些原则时,我们要求类似基本上一致通过的办法,而对这些原则的改变,我们也同样要求类似基本上一致通过的办法。
包含在我们宪法中的和包含在其他相类似的成文法或不成文法中的某些问题不采用多数裁决的原则的自我克制条例,以及在这些宪法或相应的文件中的禁止对个人施行强制办法的特殊条款,它们本身可以被看作为通过自由讨论而得到的东西,以及能反映对手段的基本一致意见的东西。
尽管我们的论述仍然是概略性的,我现在更详细地考察哪些范围完全不能通过市场来加以处理,或者哪些能够加以处理,但其代价是如此之高,以致我们宁可采用政治渠道的解决办法。
作为规则制定者和裁判员的政府
对人们日常的活动和活动在其中进行的一般习惯和法律体制加以区别是很重要的事情。日常的活动犹如游戏的参加者在游戏中的活动,而体制则犹如他们的游戏的规则。正如一场好的游戏要求双方成员遵守游戏规则和接受裁判员对规则的解释和执行那样,一个良好的社会也要求它的成员同意于支配他们之间关系的一般条件,同意于对这些条件的不同解释的一些裁决的方法,以及同意于强制执行普遍接受的规则的某些方法。在一个社会中,正和在一个游戏中一样,极大部分的一般条件是意识之外的不加思索便接受的习惯的后果。对习惯的轻微的改变最多也不过使我们对它加以具体地考虑,虽然一系列轻微的变化的累积的影响在一场比赛或一个社会的性质上可以构成游戏或社会性质的剧烈的改变。还有,在一场游戏和一个社会中,除非在大部分的时间内,大多数的参加者在没有外界制裁的情况下遵守这些规则,除非整个社会具有基本相同的意见,任何形式的规则都无法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单单依靠习惯成这种一致性来解释和实施这些规则;我们需要一个裁判员。因此,这些就是一个自由社会政府的基本作用:提供我们能够改变规则的手段,调解我们之间对于规则意义上的分歧,和迫使否则就不会参加游戏的少数几个人遵守这些规则。
在这些方面出现了对政府的需要,因为,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不论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具有多大的吸引力,但在不完善人们的世界里,它是行不通的。各个人的自由可能相互冲突。当冲突存在时,必须限制一个人的自由以便保存另一人的自由——正象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说过的那样:“我移动我的拳头的自由必须受到你的下巴的接近程度的限制。”
决定政府采取适当行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不同个人的自由之间的这些冲突。在某些情况下,回答是容易的。对于一个人谋杀他邻居的自由必须由于保存其他人生存的自由而被牺牲掉这一命题,要想取得几乎一致的意见是没有多大困难的。在别的情况下,回答是困难的。在经济领域内,关于联合自由和竞争自由之间的冲突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把“自由”来形容“企业”有什么意义呢?在美国,“自由”被理解为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来建立企业的意思。这就是说:现有的企业不能自由地排除竞争者,除非是以相等的价格出售较好的产品或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同等产品。另一方面,按照欧洲大陆的传统解释,它的意义一般是:企业有自由来做它所要做的事情,包括决定价格,划分市场以及采用别的技术以便排除潜在的竞争者。在这一领域中的最困难的具体问题来自关于劳动者的联合。在这里,联合自由和竞争自由的问题特别尖锐。
在给财产权下定义这个更为基本的经济领域中,回答是既困难又重要。正象几世纪以来的发展和体现在我们立法里那样,财产的概念已成为我们之中如此大的一个部分,以致我们趋向于把它认为是当然的,而不去辨认财产的内容和财产所有者的那些权利是复杂的社会产物而不是自行证明的命题。我的土地有所有权,以及我能任意使用我财产的自由是否能准许我拒绝另外的人乘飞机飞越我的田地呢?或者他是否有权优先使用他的飞机呢?或者这是否取决于他飞得多高呢?或者是否取决于飞机的噪音有多响呢?自愿交换是否要求他为了飞越我的田地而付款给我呢?或者我是否必须付款给他,以禁止他飞越我的田地呢?仅仅提到使用权、版权、专利权;公司的股票,河岸权,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也许可以突出地表现出在财产定义中的一般被接受了的社会规则。它也可以告诉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具体地加以规定的以及普遍被接受了的财产定义的存在,要比定义的内容远为重要。
出现特别困难问题的另一个经济领域是货币制度。政府对货币制度的责任很早已经被认识到。宪法明确规定议会有权“铸造货币,调整其价值和外币的价值”。或许没有其他经济活动的领域,在其中,政府的行动是如此一致地被接受。这种习惯性的和迄今已经几乎不加思索地承认政府的责任使我们彻底地理解这种责任具有更多的必要性,因为它增加了政府从适合于自由社会的活动扩展到不适合自由社会的那些活动的危险性,增加了从提供货币机构到决定个人之间资源的分配的危险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三章里详细地加以讨论。
总之,通过自愿交换而组织的经济活动系以下列假设条件为前提:通过政府我们提供了法律和秩序的维护,以使防止一人受到另一人的强制行为,提供了自愿参与的合同的强制执行,提供了财产权的意义的定义,提供了对这种权利解释和强制执行的办法以及提供了货币机构。
政府由于技术垄断和邻近影响而采取的行动
上面论述的政府作用是从事于一些市场本身所不能从事的事情,即:决定、调解和强制执行游戏的规则。我们也可能要通过政府做一些市场在想象上是可能做到的,而由于技术和类似的原因使这样做具有困难的那些事项。所有这一切事项可以被归结成严格地自愿交换是非常昂贵或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情况。这种情况一般有两个总的类别:垄断和类似的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邻近影响。
只有在几乎是相等的其他的选择存在时,交换才真正是自愿的。垄断意味着没有其他的选择,从而妨碍实际的交换自由。在实践上,垄断如果不是一般地那也是经常地起源于政府的支持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勾结。关于这些,问题是避免政府对垄断的扶植,或是鼓励有效地强制执行条文规定,如包含在反托拉斯法内的那些条文。然而,垄断也可能由于在技术上单一的制造商或企业效率最高而产生。我敢于指出:这些情况要比所设想的为少,但是它们无疑地会出现。一个简单的例子或许是在一个城市里的电话业务。我将把这些情况称为“技术的”垄断。
当技术条件使垄断成为市场竞争的力量的自然结果时,似乎存在着三种情况:私人垄断、国家垄断或公共调节。所有三种情况都是不好的,因此,我们必须在讲的事物中选择最好的。在美国考察对垄断的公共调节的亨利·西蒙斯发现:结果是如此地令人不满,以致于他作出结论,认为国家垄断害处较少。而考察国家对德国铁路垄断的著名德国自由主义者瓦尔特·欧肯发现:结果是如此地令人不满,以致于他作出结论,认为公共调节害处较少。研究了上述二者以后,我勉强地作出结论,认为:假使可以容忍的话,那末,私人垄断可能是害处最少的。
假使社会是静止不变的,从而导致技术垄断的条件肯定也是如此,那末,我对我的结论没有多少信心。然而,在一个迅速改变的社会中,造成技术垄断的条件经常变动,从而,我怀疑:对于这种条件的改变,公共调节和国家垄断可能比私人垄断作出较少的反应,较难于被排除掉。
美国的铁路是最好的例子。由于十九世纪的技术领域的原因,铁路的很大程度的垄断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设立州际商业委员会的原因。但是,条件起了变化。公路和空运的出现把铁路的垄断成分减少到不足道的比例。然而,我们并没有排除掉州际商业委员会。相反地,开始作为一个保护公众免受铁路剥削的机构的州际商业委员会已经成为一个保护铁路免受卡车和其他交通工具的竞争的机构。在最近,甚至于保护现有的卡车公司免受新参加者的竞争。同样,在英国,当铁路被国有化时,卡车运输业在最初也成为国家垄断。假使美国铁路从来不受公共调节,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现在的交通包括铁路在内已经是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剩余的垄断成分的一种竞争性很大的行业。
然而,在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公共调节之间的选择危害较少的一个不能一次作出决定后永远不加改变,而与客观情况无关。假使技术垄断是某种被认为是必要的劳务或商品,假使它的垄断力量是相当大的,那末,即使是短期的,私人不受调节的垄断作用可能是不可容忍的,从而,公共调节或国家垄断可能危害较少。
技术垄断有时可以用来论证既存的国家垄断的存在的必要性。它本身并不能论证通过使其他任何人与之相竞争成为非法行为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垄断。例如,没有办法来论证我们目前对邮局的国家垄断的必要性。有人可能进行争辩,认为传递邮件是一个技术垄断,而国家垄断危害最少。按照这种方法,我们或许能论证政府邮局的必要性,但不能论证当前禁止任何其他人传递邮件的法律的存在的必要性。假使传递邮件是技术垄断,谁也不能与政府进行竞争。假使它不是技术垄断,政府就没有理由经营邮局。查明这事唯一的检验方法就是让其他人自由参与这项活动。
为什么我们具有邮局垄断的历史原因,是因为骏马快递这家商业在横贯美洲大陆的邮件传递上具有如此之好的成果,以致政府在开始从事横贯大陆的邮递业务时,它不能有效地进行竞争从而亏了本。结果是制订了法律,使任何其他人传递邮件成为非法的。这就是为什么亚当斯捷运公司在今天是一家投资公司而不是一个运输业公司的原因。我推测:假使传递邮件业务对所有的人开放,就会有大量厂商参加这项工作,从而这个陈旧落后的企业就会很快地得到彻底改革。
不可能严格地自愿交换的第二种情况出现于当个人的行动对其他个人有影响,而又不能为之向他们收费或补偿的时候。这是“邻近影响”的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河流的污染。污染河流的人实际上是迫使其他人用好水来换取坏水。这些其他人可能愿意按照一定价格进行交换。但是,对单独行动的个人来说,要想回避交换或取得应有的补偿是不可能的。
【注:这种邻近影响其实就是外部性~】
较不明显的例子是公路的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在技术上是可能指出具体的个人因而向他收取使用费,于是有可能由私人经营。然而,对于具有许多出入口的人人可使用的公路而言,如果向每一个人按使用的多少收费,那末,征收的费用会是非常高的。因为,必须在所有的出入口处建立收费棚或类似的设施。汽油税是大致按照使用公路的多少向个人收费的非常低廉的一种方法。可是这种方法不能把具体的支付和具体使用紧密地连在一起。因此,使私营企业提供劳务和收取费用而不建立广泛的私人垄断是不大可能的。
这些考虑不适用于交通频繁和出入口有限的长距离的高速公路。对于这些而言,收取费用的成本是少量的,而在很多情况下,正在使用这种办法。同时,往往存在着大量的可供选择的途径,从而,没有严重的垄断问题。因而,具有充分理由来说明它们应该为私人所有并为私人所经营。在如此的情况下,经营公路的企业应该取得由于在它的公路上旅行而付的汽油税。
公园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因为它们可以说明邻近影响能否被用来作为论据的事例之间的差别。同时,也因为几乎每一个人在最初想到这个问题时总是把国家公园的经营看作显然是政府应有的职能。可是,事实上,邻近影响可以为市立公园提供存在的理由,而并不能为国家公园如黄石公园(或科罗拉多大峡谷公园)提供存在的理由。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基本的差异呢?以市立公园而论,识别从中获得好处的人们和向那些获得好处的人们收费是非常困难的事。假使一个公园位于城市中心,那四周的房屋从空旷的场地得到好处,从那里通过或从旁边走过的人们也得到好处。在各个大门口收费和对每个能眺望公园的窗户征收每年的费用需要很高的代价并且是非常困难的。另一方面,黄石公园的入口是很少的,大多数人来到公园,都得停留一定的时间,所以完全可以建立收费棚和收门票。现在的确是这样做了,虽然收费不足以维持整个的开支。假使公众对这种活动具有足够的为之而付钱的需要,那末,私营企业肯定会有积极性来提供这些公园。当然,许多这种性质的私营企业目前是存在着。我自己看不出有任何能为这个领域中的政府活动提供理由的邻近影响或重要的垄断影响。
象那些我已经放在邻近影响的标题下来考虑的事情已被使用来使几乎每一个可能的政府干涉成为合理化。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合理化是企图利用,而不是正确地使用了邻近影响的概念。邻近影响的作用是两方面的。它们能构成限制政府活动,又能构成扩展政府活动的理由。邻近影响妨碍了自愿交换,因为要鉴别对第三方的影响和衡量其大小是困难的。但是,这种困难也出现在政府的活动中。要知道邻近影响在什么时候大到足够的程度,以致值得为了克服它们而花费特殊费用是困难的,而以适当形式来分配这些费用甚至还要困难。结果,当政府从事活动来克服邻近影响时,由于它未能向私人财产收取费用或作出补偿,它将部分地造成另外的一些邻近影响。在原先的和新造成的邻近影响中究竟何者更为严重,那只能通过具体情况来加以判断。即使如此,判断也只能是大致的。此外,使用政府来克服邻近影响本身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与政府行动的特殊场合没有关系的邻近影响。政府的每一个干预行动直接限制了个人自由的范围,并且由于第一章里详尽阐述的理由而间接地威胁了自由的保存。
我们的原则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界线来规定: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来利用政府以便共同完成我们各自通过严格地自愿交换难于完成或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在任何企图干预的具体情况下,我们必须编造一个平衡表,个别地列出其优点和缺点。我们的原则告诉我们,哪几个项目放在一边,哪几个项目放在另一边。原则也给了我们一些决定各个项目的重要性的基础。特别是,我们总是要把政府干预的企图以及它威胁自由的邻近影响记在缺点的一边,并且给这个影响以相当的份量。至于给它和其他项目多少份量,得取决于具体情况。例如,假使现在政府的干涉是次要的,我们将把较小的权数给与增加政府干预的消极影响。这是为什么很多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如H.西蒙斯在那时的政府规模小于现在的标准的时候,愿意让政府从事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的活动,因为,现在的政府已经过份地扩大了。
政府根据家长主义理由而采取的行动
只有对负责任的个人而言,自由才是可以维护的目标。我们不主张对疯子和儿童的自由。在负责的和不负责的个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必须划出一条界线。然而,这意味着:在我们自由的最终目标中,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含混之处。对我们认为是不负责的那些人来说,家长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最明显的或许是疯人的情况。我们既不愿意他们有自由,也不愿意枪毙他们。假使我们能够依靠个人的自愿的活动来照顾疯人的生活,这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排除这种慈善活动不够多的可能性。不够多的原因至少在于其中牵涉到的邻近影响,即:如果另一人对照顾疯人作出贡献大,我便得到好处。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能愿意通过政府来安排疯人的照顾。
儿童提供了较为困难的情况。在我们社会中最后起作用的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然而,把家庭作为一个单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权宜之计而不是由于原则。我们相信:双亲一般是最适当的人来保护他们的孩子并且提供一切使孩子发展成为适合于自由的负责任的个人。但是我们不相信:双亲具有可以任意对待其他人的自由。儿童在胚胎中是负责任的个体,而一个相信自由的人认为:应该保护他们的最终的权利。
以不同的和似乎是生硬的方式来说,儿童同时是消费品和社会的潜在地负责任的成员。个人随意使用他们的经济资源的自由,包括他们使用资源来生育孩子的自由——好象是购买儿童劳务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消费品。但是,一旦作出了这种选择,儿童本身便具有他们自己的价值和他们自己的不单纯是双亲自由的延伸的自由。
支持政府行动的家长主义方面的理由在很多方面对一个自由主义者来说是最有问题的,因为,它涉及到承认一个原则——即:某些人可以为别人作出决定。对于这个原则在许多方面的应用,自由主义者是反对的,而且他还正确地把这原则看作为他思想上的主要对立面,这种或那种形式的集体主义的标志,不论集体主义是否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然而,假装认为问题比实际情况更为简单是无济于事的。对家长主义的办法的需要是回避不了的。正象边塞于1914年写的关于一个保护智力不健全的人的法令那样:“智力缺陷法案是沿着没有一个健全的人会拒绝进入的途径的第一步,但是假使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它会使政治家碰到如果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干预个人自由就难以克服的困难。”现在没有公式可以告诉我们应该停止在何处。我们必须依靠我们的靠不住的判断;而在一经得出判断后,我们必须依靠我们的能力去说服我们的同胞使他们相信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或者依靠他们的能力来说服我们改变我们的观点。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必须具有信心,相信不完善的和有偏见的人们会通过自由讨论和逐步地改正错误而达到一致的意见。
结 论
从事了刑事项的政府:包括维持法律和秩序、规定财产权的内容、作为我们能改变财产权的内容和其他经济游戏的规则的机构、对解释规则的争执作出裁决、强制执行合同、促进竞争、提供货币机构、从事对抗技术垄断的活动和从事广泛地被认为重要到使政府能进行干预的邻近影响的消除,同时,又包括补充私人的慈善事业和私人家庭对不论是疯人还是儿童那样的不能负责任的人的照顾——这样的政府显然可以执行重要的职能。在思想上不自我矛盾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然而,同样真实的是:这样一个政府的职能显然有限,而且会约束自己,不从事于象美国联邦和州政府以及西方其他国家的相应的机构现在所从事的那样繁多的活动。下面几章将略为详细地论述这些活动的一部分,而某几种活动已经在上面加以讨论,但是,在本章的结尾,简单地列出美国政府现在从事的而根据上述的原理我看不出有任何正确的理由来从事的某些活动也许会对自由主义所认为的政府应有的作用,提供适当的范围和比重:
1.对农业的评价支持方案。
2.进口关税或出口限制,例如当前石油进口的限额,精的限额等。
3.政府对产品的控制,例如通过农业方案或通过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对石油的摊派。
4.租金控制,如目前纽约仍然在执行的那样,或对价格和工资比较普遍的控制,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和在其后所实行的那样。
5.法定最低工资率,或法定最高价格,例如商业银行能付给活期存款的法定最高利息率为零,或者能付给储蓄和定期存款固定的法定最高利息率。
6.具体调节工业的条例,例如州际商业委员会对交通运输业的调节。当最初对铁路行使调节时,由于技术垄断的原因,调节具有某种程度的必要性,而现在,对任何交通工具都没有必要。另一个例子是对银行业的具体调节。
7.一个类似的例子。但是,由于它所含有的审查和对言论自由的侵犯而特别值得注意。它是联邦通讯委员会对电台和电视的控制。
8.目前的社会保险方案,特别是老年人和退休方案。它们实际上迫使人们(a)用他们收入中规定的部分来购买退休养老金,(b)从公众经营的企业中购买年金。
9.在不同的城市和州里对提供执照加以限制,从而把特殊企业或职位或职业限制在有执照的人的范围以内,而任何愿意参与上述活动的人在支付规定的费用以后又不一定能得到执照。
10.所谓“公共住宅”以及大量的其他津贴方案,目的在于促进住宅的兴建,如联邦住宅管理局和退伍军人管理局所保证的抵押贷款和类似的事项。
11.和平时期的征兵制。适当的自由市场的方式的安排,应该是志愿的军队,也就是说,募兵制。为了吸引需要的数量的人员,没有理由不为之而支付应有的价格。目前的安排是不公平和无原则的,它严重地干扰了年轻人形成他们生活的自由,或许甚至于比市场的代替办法要支付更大的代价。(为战时提供储备的普遍军事训练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它的必要性可以为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加以论证。)
12.上面提到的国家公园。
13.法律上禁止以营利为目标的邮件传递。
14.上面提及的为公共所有和经营的收费的公路。
这个清单是远远不够全面的。
第三章货币的控制
“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在过去几十年内已成为扩大政府干预经济事务范围的主要借口。据说,私人自由企业经济具有固有的不稳定性。听其自然,它会产生繁荣和萧条这种周期性的循环。因此,政府必须进行干预,使事态保持稳定。在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和其以后,这些论点是特别具有说服力的,并且导致这个国家执行新政和其他国家扩大类似的政府干预。近年来,“经济增长”已成为较流行的号召口号。他们争辩道:政府必须保证经济的扩展,使它为冷战提供必要的资金并且向世界上尚未表态的国家显示:一个民主的国家能比共产主义国家增长更快。
这些论点完全是错误的。事实是:那次经济大萧条象大多数其他严重失业时期一样,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当而造成,而不是由于私有制经济的任何固有的不稳定性。政府建立的一个机构——联邦储备系统——受命掌管货币政策的职责。在1930和1931年,它行使它的职责如此不当,以致把否则会是一次缓和的经济收缩转变为一场大的灾难(参阅下面在45-50页中的进一步的讨论)。同样在今天,政府的措施构成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对国际贸易的税收和其他种种限制、高额的赋税负担和复杂而不公平的赋税结构、各种调节委员会、政府对价格和工资的规定以及大量的其他措施促使个人滥用和错用资源以及使新储蓄用于不适当的投资。为了经济稳定和增长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减少而不是增加政府的干预。
减少干预仍然会使政府在这些领域具有重要作用。我们需要使用政府为自由经济制度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机构——这是提供一个稳定的法律机构的一部分职能。我们也需要使用政府来提供能使个人造成经济增长的一般性的法律和经济机构,如果增长符合于个人的价值观的话。
与经济稳定有关的政府政策的主要领域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或预算政策。本章讨论国内货币政策,下一章是国际的货币安排而第五章则为财政或预算政策。
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们的任务是沿着两个观点之间的航向前进;而这两个观点虽然都有其诱人之处,却没有一个是可以接受的。一种观点相信:纯粹自行调节的金本位制是既可能又有必要,并且相信:它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能解决在个人和国家之间促进经济合作的一切问题。另一个观点相信:为了适应不能预料的前景,就有必要赋予集中在“独立的”中央银行或某些官方机构中的一群技术人员以广泛的斟酌使用的权力。在过去,两者之中没有一个被证实为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而在将来,很可能也是如此。
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是害怕权力集中的。在一人的自由不妨碍其他人的自由的条件下,他的目标是让各个人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他相信:这个目标要求把权力分散。他对分派给政府任何可以通过市场履行的职能表示怀疑,既因为这会在有关领域中用强制手段来代替自愿合作,又因为政府作用的增加会威胁其他领域的自由。
在货币领域内,权力分散的需要引起非常棘手的问题。大家普遍同意政府必须对货币情况负责。大家也普遍承认:控制货币在造成经济活动的涨落上是一个有力的工具。
列宁的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这一格言戏剧性地表现了货币的力量。以较通俗的形式而论,货币的重要性的例证为:自古以来,货币的控制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统治者在具有议会的情况下,往往不取得议会的明确的同意而能从广大的人民那里索取到大量的钱财。从古代的君王削减硬币成份和采用相类似的办法一直到现在我们较圆滑的转动印钞机或简单改动帐目的技术,上述情况全然存在。我们的问题是要建立制度上的安排,以便使政府能对货币履行职责,然而同时还限制给与政府的权力,并且防止政府以各种方式使用这个权力来削弱而不是巩固自由社会。
商品本位
在历史上,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和几个世纪的过程中,最经常形成的一种办法是商品本位,也就是说,使用譬如象金、银、铜或铁、香烟、白兰地酒或者各种其他货物作为一些有形商品的货币。假使货币完全是由这一类有形商品组成,那末,原则上就根本不需要政府来控制。社会的货币量将取决于生产货币商品的成本,而不是其他东西。货币量的变动将取决于生产货币商品技术条件的变化和对货币需求量的变化。这是一个理想的事物,它使许多信仰自动金本位的人受到鼓舞。
真正的商品本位已经远远偏离了不需要政府干预的简单方式。历史上,在表面上能按固定比例兑换成货币商品的某种形式的信用货币已经伴随着商品本位——例如金本位或银本位——而发展出来。这种发展具有充分理由。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看,商品本位的基本缺点是它需要使用真正的资源来增加货币存量。为了在诺克斯堡或一些类似的存放黄金储备的地方重埋黄金,人们必须在南非从事辛苦的劳动把黄金从地下挖掘出来。实施商品本位,需要使用实际资源的必要性构成一个强烈的动机,使人们想方设法不使用这些资源而达到同样的结果。假使人们接受上面印有“我答应支付若干单位的货币商品”的纸张作为货币,这些纸张就能起着和有形的黄金或白银同样的作用,而需要消耗的资源就少得多。这一点我曾在别处以较大篇幅加以论述,而在我看来,它似乎是商品本位基本的困难之处。
假使自动调节的商品本位能够实现,它将为自由主义者进退两难的困境提供良好的解决办法:既有一个稳定的货币机构,而又没有不负责任的行使货币权力的危险。例如,假使一个国家的公众都支持一个地道的几乎100%的货币均由黄金组成的金本位,同时受到金本位神话的熏陶,从而相信政府干预金本位的正常运行是不道德和不应该的,该制度会提供有效的保证,使政府不能对货币胡作非为和从事不负责的货币行动。在这种本位下,政府的任何货币权力的范围是很小的。**但是,正象刚说过的那样,这种自动制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证实为是可能的。它往往倾向于向含有信用因素的混合制方向发展,例如,除了商品货币之外的钞票和银行存款,或政府的票据。一旦引入信用因素,即使信用在最初系由私人所提供,要想避免政府对它们的控制是困难的。其理由基本上是防止伪造物或在经济上的类似行为这一困难。信用货币是支付标准货币的一个契约。通常的情况是:在制订这样契约和实现这样契约之间趋向于有一个长的间隔。这便增加了执行契约的困难,因此也增加了签订欺骗性的契约的诱惑性。此外,一旦引入信用因素,诱惑政府本身去发行信用货币几乎是不可阻挡的。因此,商品本位实际上趋向于变成包含国家广泛的干预的混合本位。*8
应该指出,尽管很多赞成金本位的人发表大量的言论,而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人实际上希望有一个真正、完全的金本位。那些自己以为要求金本位的人们所指的,几乎总是当代的本位或在三十年代维持的那种受到中央银行或其他政府机构管理的金本位。这种金本位保持少量的黄金作为信用货币的“储备”——这是个非常不确切的名词。有些人确实走得很远,以致于赞成二十年代所维持的那种本位。在那个年代里,实际上是黄金或黄金证券作为在人手之间流通的货币——某种金币本位。但是,即使是这些人也赞成和黄金共存的政府信用货币再加上以黄金和政府信用作为部分储备的银行所造成的存款。甚至在所谓十九世纪金本位的大好日子里,那时英格兰银行被认为是正在熟练地经营金本位时,货币制度也远非是一个自行调节的金本位。甚至在那时,也是一个高度受到管理的本位。当然,由于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采用了政府对“充分就业”有责任的观点,目前的情况更甚于此。
我的结论是:对于建立一个自由社会的货币的安排而论,自动调节的商品本位既行不通,又不是解决的办法。它并不理想,因为,它造成生产货币商品所需的大量资源的费用。它行不通,因为,使它能生效的神话和信念并不存在。
这个结论不仅能为有关的一般历史资料所证实,而且也为美国的特殊经验所证实。从美国在内战后恢复黄金支付的1879年起一直到1913年,美国都使用金本位。尽管比我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完全自动的金本位。这种金本位还是远远不是100%的金本位。在上述的情况中,政府发行了纸币,而私人银行以存款形式发行了国家的大部分的有效的流通媒介物。银行受到政府机关的严格的管理——国民银行由货市监察官员所管理,州银行由州银行官方当局所管理。不管黄金是否以硬币或黄金证券的形式而为财政部、银行、或个人直接所有,黄金占有货币总量的10-20%之间,其确实的百分比随着时间的转移而有所不同。剩下的80—90%则由白银、信用货币和没有相等数量的黄金来支持的银行存款所组成。
我们回顾起来,该制度似乎发挥了相当好的作用。对于那时的美国人来说,显然并不如此。以布赖恩的关于黄金十字架演说为高潮,并作为1896年选举的关键问题的八十年代鼓吹白银的运动就是一种不满的象征。这个运动又应对九十年代早期严重的经济萧条的年月负主要责任。这个运动引起广泛的恐惧,耽心美国会脱离金本位,从而美元和外币的比价就会贬值。这导致了迫使国内通货紧缩的美元外流和资金外流。
1873、1884、1890和1893年连续不断的金融危机造成了商业和银行界对银行业改革的广泛要求。1907年涉及银行界一致拒绝把存款换成随时可提取的现款的恐慌最后把对金融制度的不满转变成为迫切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想法。议会建立了国家货币委员会,而该委员会在1910年的报告中的建议被体现在1913年通过的联邦储备法令内。按照联邦储备法的方针进行的改革得到了社会上各方面的支持,从工人阶级到银行界以及两大政党都是如此。国家货币委员会的主席是共和党员纳尔逊·W·奥尔德里奇,而对联邦储备法负主要责任的参议员是民主党员卡特·W·格拉斯。
联邦储备法所造成的货币安排的变化实际上要比该法的创建者或支持者所预期的远为强烈。在储备法通过时,金本位牢固地统治着全世界——它不是一个完全自动的金本位,但要比任何一切我们迄今经历过的远为接近于理想。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金本位会继续这样统治下去,从而联邦储备系统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储备法刚一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即爆发。于是出现大规模地放弃金本位。到大战结束时,联邦储备系统不再是用来保证一种形式的货币转变为其他形式的货币以及管理和监督银行金本位的一个不重要的附加物。它已成为能决定美国货币量和影响全世界的国际金融情况的一个有自行运用的权力的权威机关。
有自行运用权力的货币权威
至少是从内战时国家银行法公布以来,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是美国货币机构最值得注意的变化。由1836年美国第二银行的营业执照期期满开始,它第一次建立一个单独的官方机构,其明确的职责为对货币情况负责,并且具有适当的权力来取得货币情况的稳定或者至少防止过分不稳定的情况。因此,全盘地比较该制度成立和成立后的客观事实是有用处的——譬如说,从内战刚结束到1914年和从1914年到今天这两个长度相等的时期。
第二个时期在经济上显然是更不稳定的,不管是以货币数量、以价格还是以产量来衡量,都是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在第二个时期过程中的较大的不稳定性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不管我们的货币制度如何,这些显然会是不稳定性的源泉。但是,即使略去战争和战事刚结束那几年,而仅仅考虑和平的年代,譬如说,从1920年到1939年和从1947年到今天,结果还是一样。货币数量,价格和产量在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之后肯定比以前更不稳定。当然,产量最不稳定的时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包括1920——1921年、1929-1933年和1937-1938年的几次严重的商业收缩期。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其他的二十年包含多至三个这样严重的商业收缩期。
这种粗略的比较当然并不能证明联邦储备系统无助于货币稳定。或许联邦储备系统必须处理的问题要比那些冲击早期货币结构的问题更为严重。或许那些问题在早期安排的情况下会产生更大程度的货币不稳定性。但是,这种粗略的比较至少可以使读者思索一下,而不象往常的情况那样,认为一个象联邦储备系统那样长期成立的、那样有权力的、那样影响广泛的机构一定会在执行必要的和意图中的职能中并且对为之而建立的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
根据对大量历史资料的研究,我个人相信:通过粗略的比较所显示的经济稳定性的差异,确实应归因于货币机构的不同。这些例证使我相信:在第一次大战中和刚结束后,至少三分之一的价格上升应归因于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而且上升根本不会发生,假使以前的银行制度被保留下来的话。它们使我相信:每次主要的经济收缩期的严重性——1920-1921年,1929-1933年和1937——1938年——应直接归因于联邦储备系统的成立和它的当局的疏忽,而在以前的货币和银行的安排之下,这些事实不会发生。在这些或那些情况下,可能会有经济衰退,但却不大可能发展成为主要的经济收缩。
我显然不能在此提出这种例证。然而,由于1929—1933年的大萧条在形成——或者可以说,歪曲——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的一般态度的重要性,对于根据事实而作出的解释作比较全面的说明会是有价值的事情。
由于它的戏剧性的特点,1929年10月股票市场的崩溃结束了1928年和1929年的多头市场这一事实常常被看作为既是大萧条的开端,又是大萧条的主要近因。两者都是不正确的。经济活动的高峰为1929年中期,距那次股票市场的崩溃尚有几个月。高峰之所以可能象上述时期那样早地到来,其部分原因在于联邦储备系统企图减少“投机”而造成的货币紧缩的情况——以这种间接的方式,股票市场可能在导致紧缩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反过来,股票市场崩溃毫无疑问地对经济情况的信心和个人花钱的意图有一些间接影响。这些影响对经济活动的进程起着抑制作用。但是,单靠这些影响自己不可能造成经济活动的崩溃。它们至多只能使收缩期稍为长些,而且使它比在美国历史上干扰经济增长的缓和的一般衰退更为严重。它们不会使之成为象实际情况那样的一次灾祸。
大致在第一年中,经济活动的收缩并没有显示出将支配它以后的实际过程的那些特征。经济活动的下降比大多数的经济收缩的第一年的情况更为严重,很可能是由于股票市场的崩溃,再加上自1928年年中以来一直维持的不寻常的货币紧缩情况。但是,它并没有显示出质上的不同特性,也没有显示出要退化成为一场主要的灾祸的征兆。除了根据天真的“在此之后,因之必然由于此”的逻辑推理以外,在譬如说1930年9月或10月,经济情况中没有任何东西使得以后几年的连续而猛烈的下降成为不可避免,或甚至于成为有很大的可能性。回想起来,联邦准备系统显然早已应该采取和实际做的有所不同的行动。它显然不应该允许货币数量从1929年8月到1930年10月下降几乎为3%——除了最严重的经济活动的收缩以外,比以往的任何收缩的全部期间的下降还要大。虽然这是一个错误,它或许是可以宽恕的,肯定不是关键性的。
1930年11月,当一系列的银行倒闭导致广泛的银行挤兑,也就是说,存款者企图把存款兑换成现款时,收缩的性质起了剧烈的变化。这一情况从国家的一个部分蔓延到另一部分,并且在1930年12月11日美利坚银行倒闭时达到了最高峰。这次倒闭是关键性的,不但因为美利坚银行是本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具有两亿以上的存款,而且也因为虽然它是一个普通的商业银行,它的名称使得国内的许多人和国外的甚至更多的人往往把它看作为是一个国家的官方的银行。
在1930年10月以前,没有流动性危机的征兆,或者没有对银行丧失任何信心。从这时起,流动性危机一再出现。银行倒闭的浪潮在一段时间内减少,然后又突然出现。这时,几次突出的银行倒闭事件或其他事件造成了对银行制度的缺乏信心,从而一系列的新的银行挤兑。这些是很重要的,不仅因为或主要因为银行倒闭的本身,而且也因为它们对货币数量的影响。
在象我们那样的部分准备金的银行制度里,银行当然并不具备与一美元存款相应的一美元货币(或它的等价物)。这就是为什么“存款”是如此令人误解的一个术语。当你在银行里存放一美元的现金时,银行可能在它的现金上加15或20分。一元存款的其他部分银行将通过另一种业务形式借出去。借款者可以再把现金存入这个或那个银行,而这一过程可以重复进行。结果是:对于银行拥有的每一美元现金,银行要欠几美元的存款。因此,对一定量的现金来说,人们愿意以存款的形式保存的货币的比例越高,货币数量的总额——现金加存款——越大。大量的存款者要“得到他们的现款”的企图势必意味着整个货币数量的缩减,除非使用某些方法创造出额外的现金,并且使银行得到这些现金。否则,由于企图满足存款者兑换现款的需要,一家银行会收取放款、出售票据或兑换它自己的存款从而对其他银行施加压力。其他银行反过来也会对更多的其他银行施加压力。这种恶性循环,假使听任其自行继续下去的话,会愈益严重,因为,银行想得到现金的企图迫使有价证券的价格下降,使得本来是完全健全的银行破产,动摇存款者的信心,从而,恶性循环再度开始。
在联邦储备系统成立以前,类似上述种种造成了银行业的恐慌,和象1907年那样一致性的停止存款的兑现。这种停止兑现是一个猛烈的步骤,而在短期内会使事态恶化。但它又是一个治疗措施。由于阻止事态的扩散,由于使少数银行的破产不能对其他银行产生压力从而不能导致本来是健全的银行的倒闭,它截断了恶性循环。在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中,当形势稳定下来以后,停止兑现可以解除,经济活动的恢复可以开始而又没有货币收缩。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建立联邦储备系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处理这样的事态。假使社会上出现了对货币而不是存款的大量需求,储备系统赋有权力来创造出更多的现金,同时也赋有各种手段,以便以银行的资产来担保使银行得到现金。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期望避免任何严重的危机,同时避免停止存款的兑现以及完全避免货币危机所产生的抑制经济活动的影响。
这种权力的第一次的使用机会从而也是第一次对它们的效果的检验出现于1930年11月和12月,这时,上述一系列银行倒闭已经产生。对储备系统检验得到惨重失败的结果。它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为银行系统提供流动性的现金。它显然把银行倒闭看作为不要求特殊行动的事件。然而,应该强调指出:储备系统的失败是意志的失败,而不是权力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中,正如在以后的一些情况一样,储备系统有足够的力量来为银行提供它们存款者需要的现金。假如做了这些事情,银行倒闭会被制止而货币崩溃会得以避免。
银行倒闭的初期浪潮平息下来,而在1931年早期,存在着恢复信心的苗头。联邦储备系统利用这次机会来减少它自己现有的债务——也就是说,它从事轻度的通货收缩行动来抵消自然的扩大经济活动的力量。即使如此,不但在货币方面,而且在其他经济活动方面,显然具有改进的征兆。假使不管其后的那些事实,1931年最初的四、五个月的数字具有一个周期底部和复苏开始期所有的特征。 然而,暂时性的复苏时期是短促的。重新开始的银行倒闭引起了另外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并且再次导致货币数量的重新下降。联邦储备系统再次置若罔闻。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商业银行系统对于现款的需求,在作为“借款的最后支柱”的联邦储备系统的帐簿上,它的商业银行成员可能得到的信用呈现出下降的数字。
1931年9月,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在这个行动的前后,黄金均从美国被提走。虽然黄金在前两年中流向美国,而且美国黄金存量和联邦储备的黄金储备比例处在最高点,储备系统对黄金流向国外作出猛烈和迅速的反应,正和它对过去的国内的信用收缩的态度相反。它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以致肯定会加强国内金融的困难。在两年多严重经济活动的收缩之后,储备系统提高贴现率——该系统借款给商业银行成员的利息率——的幅度比它在过去和将来的整个历史中的同一短暂时间里提高的幅度要大。这个措施阻止了黄金外流。伴随它而来的是;银行倒闭数量惊人的增加和银行挤兑。从1931年8月到1932年1月的六个月内,当时的每十个银行中约有一个停止营业,而商业银行的总存款下跌了15%。1932年买进几亿美元的政府债券这一暂时的政策的改变使下降的速度放慢。假使1931年采取同一措施,它几乎肯定足以防止上述的崩溃。到1932年,事态已经被推迟到无法挽救的地步,而当储备系统又回到它的消极状态时,在暂时性的好转之后,重新出现了以1933年的银行放假而告终的崩溃——那时,美国每一个银行正式关门一个星期以上。主要为防止暂时中止把存款兑换为现款而建立的制度——暂时中止把存款兑换为现金在以前是使银行免于倒闭的一个措施——在起初竟然听任全国几乎三分之一的银行垮台,然后又赞成一个远比任何过去更加广泛和严格的中止兑换的措施。虽然如此,自我辩解的能力是如此之大,以致联邦准备局能在它1933年的年度报告里写着:“联邦储备银行在危机期间满足货币大量需求的能力表明了在联邦储备法案之下的国家货币制度的有效性质。……假使联邦储备系统不采用灵活的公开市场购买的政策,很难说这次经济危机会发展成为什么样子。”
总的说来,从1929年7月到1933年3月,美国的货币数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其中的三分之二以上出现于英国脱离金本位之后。假使货币数量象它显然能够和应该那样保持不变,经济活动的收缩不但会比较短暂而且要远为缓和。它和历史上的收缩相比,可能仍然是比较严重的。然而,假使货币数量没有下降,我们很难设想:在四年之中,货币收入能下降一半以上,而价格能下降三分之一以上。据我所知,没有任何国家在任何时间有过任何严重的经济萧条而又不伴随着货币数量的急剧下降;而同样的,没有任何货币数量的下降而又不伴随着严重的经济萧条。
美国的经济大萧条远远不是私有企业制度所固有的不稳定性的象征,而却可以证明:当少数人对一个国家的货币制度拥有巨大的权力时,他们的错误可以造成多么大损失。
也可能认为:有鉴于那时的知识水平,这些错误是可以宽恕的——虽然我并不那样想。但是,这在实际上是与题无关的。**凡是赋予少数人如此大的权力和如此多的伸缩余地以致其错误能有如此深远影响的任何制度都是一个坏制度——与错误是否可以宽恕无关。对相信自由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坏的制度,其原因在于:它赋予少数人这样的权力而没有对它施加限制的政治机构——这是反对“独立的”中央银行制度的关键性的政治论点。但是,即使对那些认为安全高于自由的人来说,它也是一个坏制度。不管是否可以宽恕,在一个分散责任而却把大权赋予少数人从而使重要政策行动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带有偶然性的个人性格和作风的这一制度中,错误是不能避免的。这是反对“独立的”中央银行制的关键性的技术性的论点。用克莱门梭的话来说,货币重要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不能让它为中央银行所管理。
用规章来代替官方当局
假使我们想达到我们的目标而不依赖于完全自动调节的金本位的作用,也不给予有自主权的当局以广泛的处理问题的权力,我们怎么能建立一个既稳定、同时又不受不负责任的政府的摆布,既能对自由企业经济提供必要的货币体系、而又不可能被用来作为威胁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权力的货币制度呢?
这个提出的唯一有希望的方法是通过立法而成立一个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人治的政府来执行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能使公众通过政治当局对货币政策进行控制,同时又可使货币政策不受政治当局的经常出现的胡思乱想的支配。
为货币政策制定管理的规章的争论之点初看起来很象完全不同的一个论题,即:宪法第一次修正案的争论。不论何时有人建议用制定的规章来控制货币时,典型的一套的回答是:以这种方式来捆住货币当局的手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假使货币当局愿意的话,它总是能凭自己意愿做规章要求它做的事情。除此以外,它还有其他的选择,因而,据说它“肯定”能比规章做得更好。同一论点的另一说法是把上述论点应用于条例的制定。假使议员们同意制定一个规章,那末它肯定也会同意为每一个特殊的情况制定“正确的”政策。既然如此,有人又会说:采用规章的办法又怎么能为免于受到不负责任的政治行动提供任何保证呢?
只要在用语上稍加改变,同一个论点也能适应于宪法第一修正案,并且同样地适应于整个的《权利法案》。人们可能会说,为对言论自由的干预制定一个统一的禁令不是太荒谬吗?为什么我们不根据每一件事例的情况分别加以处理呢?这不是那个同一的在货币问题上的论点重新出现吗?这个论点不是认为:不应该事先捆住货币当局的手脚,而应该让它根据每一件事例的情况分别加以处理吗?为什么这个论点对言论自由不能同样有效呢?一个人想站在街角拐弯处提倡节制生育,另一个想提倡共产主义,第三个想提倡素食主义等等,直至无穷。为什么对每一个人不制订一个法律来肯定或否定他散播特殊观点的权利呢?或者,为什么不选择其他办法,把裁决问题的权力给予一个行政机构呢?显而易见,假使我们根据每一个事例的情况加以处理,大多数人几乎肯定会在大多数情况下投票来否定言论自由,甚至于或许在个别地处理时去否定每一个事例。对X先生是否应该传播节育的投票几乎肯定会造成大多数的反对票,而对宣传共产主义的投票也会如此。素食主义或许能够通过,虽然这一结果并不肯定。
但是现在,设想把所有这些情况合并在一起,并且要求公众对合并在一起的情况投票,要求对言论自由是否应该在所有情况下予以否定,还是肯定。完全可以设想而我认为有很大可能的是:绝大多数人会投票赞成言论自由,而对合并起来的情况,人们会投与对单个情况投票方式截然相反的票。为什么?原因之一在于:当一个人处于少数派时,他对被剥夺掉他言论自由权的感受大于他处于多数派时剥夺掉其他人的言论自由权的感受。由于这个原因,当他对合并在一起的情况进行投票时,他对在他处于少数派时少量的被剥夺掉言论自由的情况所感到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他经常剥夺掉别人言论自由的情况所感到的重要性。
另一个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比较大的理由是:假使把合并在一起的情况全盘地加以考虑,显然可以看到,被执行的政策具有全面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在对单一的情况投票时是既看不出来而又应加以考虑的。在对琼斯先生是否能在街角发言进行投票时,我们不能计入言论自由的一般政策的有利影响。我们不会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个没有经过特别的批准人们不能自由地在街角发言的社会是一个为众所知的新思想、新实验、新变革等等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的社会,从而,我们感谢我们的好运气能居于一个采用自我克制的而又不单独考虑每一个言论自由事例的社会。
完全相同的考虑适用于货币领域。假使每个情况均根据它本身的情况而加以考虑,那末,在大部分的事例中,就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决定,因为,决策者仅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考虑,而没有照顾到政策的全面后果。另一方面,仅使对一组合并在一起的情况采用一般性的规章,那末,规章的存在本身会对人们的态度、信念和希望产生有利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是即使在对一系列的个别情况采用完全相同的政策时所考虑不到的。
假使需要制定规章的话,应该制定什么样的规章呢?一般有自由主义见解的人最经常提出的规章是物价水平的规章,即:立法机关制定的给予货币当局的维持稳定价格水平的指示。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规章。这是不好的规章,因为,它使用了货币当局本身的行动没有明确和直接的权力来完成的目标。结果,它使责任分散,并且留给官方当局过多的回旋的余地。在货币变动和物价水平之间无疑地具有密切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不密切、并不经常、和直接到如此的程度,以致达到稳定价格水平成为货币当局的日常活动的合适的一个指标。
关于采用什么规章的问题,我已经在别处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所以,我在这儿只限于叙述我的结论。根据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以我看来,按照货币数量的变化来制定规章似乎是可取的。我目前的主张是由立法机关制定规章,命令货币当局来使得货币数量按照具体的比例增长。为了这个目的,我的货币数量的定义包括商业银行以外的流通中的货币加上商业银行的全部存款。我认为:应该指令联邦储备系统,尽可能地使上述定义的货币数量的总额逐月甚至逐日地按照年率为3-5% 之间的比例增长。只要始终遵循一个定义和一个增长率,选择哪一个定义或哪一数值的增长率不过是次要的问题。
按照目前的情况,虽然这个规章会剧烈地削减货币当局的自行处理事务的权力,关于如何使货币数量保持在规定的比例、债务处理、银行监督以及其他等等方面,它仍然留在联邦储备系统和财政当局手中它们所不应有的数量的自行处理问题的权力。我在别处曾经详细说明:银行及财政的进一步改革是可能的和应该做的。它们会对目前政府干预贷款和投资活动造成消除的影响,并且会把政府的财政从作为长期的不稳定和变化无常的根源的情况转变成为相当规则的和可以预测的活动。虽然这些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它们远比对货币数量采用规章以便限制货币当局的自行处理问题的权力这一事项具有较少的根本性的意义。
我要强调指出:我并不把我的具体建议当作为货币管理的包罗一切和囊括一切的规章,从而,应该以某种方式被刻在石碑上以备将来的遵崇之用。在我看来,它似乎是一个根据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而能提供一定程度的货币稳定性的最有希望的规章。我希望:随着我们对这个规章的使用,随着我们懂得更多的关于货币的知识,我们还可能设计出更好的能得到更好结果的规章。在我看来,上述规章是当前唯一可行的办法,以便把货币政策转变成为自由社会的一个支柱,而不是对自由社会基础的威胁。
第四章国际金融和贸易安排
国际货币安排问题是不同国家的货币之间的关系:在何种比例和条件下,个人能够把美元兑换成英镑,把加拿大元兑换成美元,等等。这个问题和前一章讨论过的货币控制有密切联系。这也和政府的国际贸易政策具有联系,因为,控制国际贸易是影响国际支付的一种办法。
国际货币安排对经济自由的重要性
尽管它具有技术性和难于克服的复杂性,国际货币安排这个论题是自由主义者不能忽略的一个主题。当我们说:对今天美国经济自由最严重的短期威胁——当然,除了由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外——是我们将被引导到采用有深远影响的经济控制以“解决”收支平衡问题。对国际贸易进行干预看来似乎是没有害处的;它们会得到在其他情况下会惧怕政府干预经济事务的人的支持。好多工商业者甚至于把它们看作为“美国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然而,很少有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情况能够扩散得如此之远,从而最后对私有企业具有如此之大的破坏性。大量的经验告诉我们,把市场经济转变成集权主义的经济社会的最有效方法是从直接控制外汇开始。这一步骤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进口的定量配给、对使用进口货的国内生产加以控制或对进口货的代用品的国内生产加以控制、如此等等无穷尽的越来越恶化的连锁反应。尽管这样,甚至于象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那样的自由企业的战士,在讨论所谓“黄金外流”时,有时也被引导到对外汇交易施加限制是一种必要的“治疗手段”的主张。这种“治疗手段”远比疾病本身更为怨劣。
在世界上的经济政策中,很少有任何真正新的东西。被断定为新的东西最终被证实为前一世纪抛弃的东西的稍加改装的形式。然而,除非我认识错误,全面的外汇控制和所谓“货币的不能兑换的性质”是一个例外,而它们的起因显示了它们集权主义的内容。就我所知,它们是在纳粹统治的早期为雅尔玛·沙赫特所发明。在过去很多情况下,货币当然曾被说成为是不可兑换的。但是,在那时,这个名词的意思是:当时的政府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以法定的比例把纸币兑换成黄金或白银、或所应兑换到的货币商品。它很少会指一个国家禁止它的市民或居民用那个国家的货币单位来表示的一定数额的纸币来换取用另一个国家货币单位表示的相应的纸币——或者换取硬币或金条。例如,在美国内战期间和其后的十五年,美国货币在拥有钞票的人不能从财政部那里把它兑换成固定数量的黄金这个意义上是不能兑换的。但是,在整个时期,他可以使用美国纸币按市场价格自由购买黄金,或按照双方同意的任何价格买卖英镑。
在美国,自从1933年以来,在过去的意义上来说,美元是不可兑换的。美国公民拥有黄金或买卖黄金是不合法的。在新的意义上来说,美元不是不可兑换的,但是,不幸的是:我们似乎正在采取非常可能地要把我们早晚赶往那个方向的政策。
黄金在美国货币制度上的作用
只有文化上的落后才能使我们仍然认为黄金是我们货币制度的核心因素。黄金在美国政策上的作用的较为正确的说法为:它主要是一种其价格受到维持的商品,象小麦或其他农产品那样。我们对黄金价格的支持方案与我们的小麦价格的支持方案在三个方面有所不同:第一,我们对外国人和国内生产者都按照支持的价格来偿付;第二,我们按照支持价格仅随意出售给外商而不出售给本国商人;第三点是黄金的货币作用的一个重要残余物。财政部有权创造货币来支付它购买的黄金——好家印刷纸币一样——因此,购买黄金的费用在预算中并不出现,而需要的金额并不一定来自国会的拨款。同样,当财政部出售黄金时,帐面上只表现为黄金证券的减少,而不是进入预算的一笔收入。
当黄金价格最初在1934年被规定在目前的35美元一盎司的水平时,这个价格远高于自由市场的黄金价格。结果,黄金大量涌进美国,在六年内,我们的黄金存量三倍于往昔。我们渐渐拥有世界黄金存量的一半以上。我们累积了“剩余”黄金,其原因和我们累积了“剩余”小麦一样——因为政府愿意支付的价格高于市场价格。最近,形势起了变化。当法定的黄金价格仍然处于35美元时,其他货品的价格变为两倍或三倍于往昔。因此,现在35美元要小于自由市场应有的价格。结果,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短缺”而不是“过剩”的问题,其原因正和限制租金上升不可避免地造成房屋“短缺”一样——因为,政府正在设法把黄金的价格维持在低于市场价格的水平。
法定的黄金价格应该在很久以前加以提高——正象小麦价格在过去经常被提高一样——除了偶然的情况的考虑,即:黄金的主要生产者,从而是价格提高的主要受益者为苏联和南非。对这两个国家,美国在政治上是最没有感情的。
政府控制黄金价格和自由经济是不相调和的,其不相调和的程度不亚于控制任何其他价格。这种假的金本位必须和真正金本位下的黄金作为货币严格地区分开来。真正的金本位和自由经济是完全调和的,虽然它可能行不通。当罗斯福政府提高黄金价格时,它在1933和1934年采取的有关的措施在基本的观点上背离了自由的原则并且创造了以后给自由世界带来灾祸的先例,其影响甚至超过规定价格这一事实本身。我指的是黄金存量的国有化,禁止为了货币目的而为私人占有的黄金,以及在国家和私人契约中废除黄金条款。
1933年和1934年早期,法律要求拥有黄金的私人把他们的黄金移交给联邦政府。政府则以相等于以前的法定价格来补偿他们,而这一法定价格在那时肯定低于市场价格。为了使这一要求有效,在美国国内拥有黄金被认为是非法的,除了用于艺术上的黄金以外。人们很难设想一个对自由企业社会赖以存在的私人财产原则有更大的破坏性的措施。按照人为规定的低价使黄金国有化同菲德尔·卡斯特罗按照人为规定的低价使土地和工厂国有化在原则上是没有差别的。美国在本身从事其中的一个以后又有什么理由来反对另一个呢?然而,关于涉及到黄金的事件,有些自由企业的支持者的盲目性是如此之大,以致在1960年,亨利·亚历山大,接替J.P.摩根公司的摩根保证信托公司的首脑,提出建议,把美国公民私人拥有黄金的禁令范围扩大到国外拥有的黄金!它的建议被艾森豪威尔总统所采纳,而银行界人氏几乎没有提出抗议。
虽然为了货币的目的而“保存”黄金被当作为借口,禁止私人拥有黄金并不是为了任何这样的货币目的而实施的,不论这个目的本身是好还是坏。实施黄金国有化目的在于使政府从黄金价格的提高中获得全部“帐面上的”利润——或者为了防止私人从中获利。
废弃黄金条款具有类似的目的,这也是破坏自由企业基本原则的一个措施。在完全理解的条件下,双方诚心诚意缔结的契约,为了一方的利益而被宣布为无效。
目前的支付和资金外流
在更加一般的水平上来论述国际货币关系,就有必要来区别两个相当不同的问题:国际收支平衡表和黄金外流的危险。两个问题之间的差异能够最简单地通过考虑一个普通商业银行的事例加以说明。银行必须以如此的方式安排其事务,以致它所收进的款项,如手续费、贷款利息,等等,多到足以支付它的开支——工资和薪金、借款的利息、办公费用、股东的收益,等等。也就是说,它必须争取一个足够大的收入帐目。但是,一个收益帐目很不错的银行仍然可能遭受严重的困难,假使由于任何原因,它的存款者对它丧失信心,而突然同时要求把他们的存款兑现的话。很多健全的银行由于在前一章里所叙述的流动性危机期间这样一种挤兑而被迫倒闭。
这两个问题当然不是没有关系的。银行的存款者对它失去信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银行的收入帐目遭受损失。然而,这两个问题又是非常不同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收入帐目的问题一般出现较慢,而有着相当长的时间来解决它们。它们很少会出其不意地来到。另一方面,挤兑可能会突然地和无中生有地冒出来。
美国的情况是完全相类似的。美国居民和美国政府本身企图以美元购买外汇,以便在别的国家中购买物品和劳务、在外国企业中进行投资、支付借款利息、偿还借款或给别人送礼;不论就私人还是公家而言,都是如此。同时,为了相应的目的,外国人也企图用外币来购买美元。事后,用来换取外币的美元数目恰好等于用外币购买的美元数目——正如售出的鞋子数目恰好等于买进的鞋子数目一样。算术就是算术,一个人购买的是另一个人出售的。但是,却没有东西来保证:按照美元表示的外币价格,某些人要花费的美元数将等于其他人要购买的美元数——正象没有东西来保证:按照任何规定的鞋价,人们要买的鞋子数正好等于其他人要出售的鞋子数一样。事后的等同反映了消除任何事前的差距的某些机制。为了这个目的而得到一个适当的机制的问题相当于银行收入帐目的问题。
此外,美国也具有一个类似银行回避挤兑的问题。美国已经承担义务,按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向外国中央银行和政府出售黄金。外国中央银行、政府和居民在美国拥有大量的款项,其形式为银行存款或能立即变卖成美元的有价证券。任何时候,持有这些款项的人可以通过把美元兑换成黄金的行为对美国财政部造成挤兑风潮。这正是1960年秋天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在将来的不可预测的日子里很可能再要发生的事情(或许会发生在本书出版以前)。
这两个问题在两方面具有联系。首先,正和银行一样,收入帐目的困难是对美国能遵守诺言按35美元一盎司价格出售黄金的能力失去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实际上一直必须向国外借款以便使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帐目保持平衡这一事实是为什么美元持有者有兴趣把美元换成黄金或其他货币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黄金的固定价格是我们用来规定另一批价格的办法——按外币计算的美元价格——而美元的流出是我们用来解决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事前矛盾的办法。
取得国际收支平衡的另一机制
如果我们考察取得国际收支平衡的其他的一些机制,我们对上述两种关系会有较清楚的理解——从许多方面来看,第一个问题是两个问题中的比较基本的一个。
假设美国在国际收支上大致保持平衡,而某种事态的出现改变了这个形势,譬如说,相对于美国居民想要出售的美元而言,外国人减少了想要买进的美元数量;或者,从另一方面来看,相对于外币持有者想要出售外币换取美元的数目相比,美元持有者想要买进的外币数量增加。这就是说,某种事态的出现可能在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造成“赤字”。这可能来源于国外生产效率的增长或国内效率的减退,可能来源于美国援外开支增加或其他国家开支的减少,或经常会遇到的千千万万种其他的变化。
对于这种干扰,国家仅有四种进行调整的方法,它必须使用这些方法的某种配合方式:
1.美国外币储备可以由于支取而减少,或外国的美币储备可以增加。在实践上,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使它的黄金储备下降,因为黄金可以兑换成为外币,或者它可以借进外币并使它们按官价和美元相交换;或者,外国政府可以按官价出售外币给美国居民从而累积美元。依赖外币储备显然最多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权宜之计。正是由于美国广泛地使用这个权宜之计才造成人们对它的国际收支的平衡的焦虑。
2.可以迫使美国国内价格作出相对于外国价格的降低。这是在纯粹的金本位下主要的调整机制。最初的赤字会造成黄金外流(见上面机制1);黄金外流会造成货币数量的下降;货币数量的下降会造成国内价格和收入的下降。同时,相反的影响会在国外出现:黄金流入会扩大货币数量,因而提高价格和收入。美国价格的降低和外国价格的上升会使美国货品对外国人更有吸引力,从而提高他们想要购买的美元数量;与此同时,价格的变化会使外国货对美国居民更少吸引力,从而降低了他们想要出售的美元数量。两者的影响都在于减少赤字,从而在没有必要进一步使黄金外流的情况下,恢复国际收支的平衡。
处于现代的管理本位之下,这些影响不是自动发生的。黄金外流可能作为第一步仍然出现,但是,它们不会在流出国中,也不会在流入国中影响货币数量,除非两国货币当局作出如此的决定。今天在每个国家中,中央银行或财政部有权抵销黄金流动的影响,或者有权在没有黄金流动的情况下改变货币数量。因此,只有在遭受赤字的国家当局,为了解决它的国际收支问题而愿意造成通货收缩,从而造成失业,或者得到盈余的国家当局愿意造成通货膨胀时,这种机制才会被使用。
3.正如通过国内价格的变动一样,通过外汇率的变动可以达到完全相同的效果。例如,假设在机制(2)下,美国一辆某种牌子的小轿车的价格下跌10%,从2800美元跌到2520美元。假使英镑的价格始终保持在2.80美元,这意味着英国的价格(不算运费和其他费用)将从1000镑跌到900镑。假使一镑的价格从2.80美元上升到 3.11美元,英国价格也会发生完全一样的跌落而并不需要美国的价格有任何变化。在过去,英国人必须花1000镑换取2800美元,而现在他只要花900镑就可以得到2800美元。他不会知道这种成本的减少和外汇率不变的情况下由于美元价格跌落而造成的成本的减少之间的区别。
实际上,外汇率的变化具有几种方式。在目前的许多国家使用的固定汇率的情况下,它能通过贬值或升值而发生变化,这就是说,政府声明:它将改变它过去规定的外汇比价。另一方面,外汇率根本不需要加以规定。它可以是天天变化的市场的外汇率,正和1950年到1962年加拿大的情况一样。假使这是市场的外汇率,它可以主要由私人交易所决定的真正的自由市场外汇率,如从1952年到1961年间的加拿大的外汇率一样,或者,它可以为政府在市场上所操纵,如英国1931 - 1939年的情况,和加拿大在1950 - 1952年以及1961-1962年的情况。在所有这些手段中,只有自由浮动外汇率才是完全自动调节和不受政府控制的。
4.机制2和3所作出的调整包括由于内部价格或由于外汇率的变化所导致的商品和劳务流动量的变化。另一种办法是:可以使用政府对贸易的直接控制或干预来减少美国企图花费的美元和扩大美国的收入。可以提高关税来阻止进口,可以使用津贴来刺激出口,可以对各种物品施加进口限额,可以控制美国公民或公司在国外的投资,等等,一直到一整套外汇控制的办法。在这个范畴之内,不但必须包括对私人活动的控制,而且还包括旨在于使国际收支平衡的政府方案的变化。可能要求外援的接受者把援助的款项在美国使用掉;武装部队为了节约“美元”,可能以较大的代价不是从国外而是从美国来购买物品——这里使用自相矛盾的字眼——以及其他种种令人感到困惑的办法。 值得注意的重要事情是:将要而且必须使用这四种办法中的一个。复式簿记必须平衡。支出必须等于收入。唯一的问题是怎么做到这一点。
我们发表的国家政策曾经是和继续会是我们不做这些事情。在1961年12月对全国制造商协会的讲演中,肯尼迪总统说,“因此,在本届政府的任期内——我重复这一点,并且使它成为一个直截了当的声明——没有施加外汇控制、使美元贬值、树立贸易障碍或中止我们经济的恢复的企图。”作为一个逻辑问题来考虑,这句话使得仅为两个可能性剩了下来:使其他国家采取我们难以依赖的有关措施,或减少总统和其他官员反复声明不准继续减少的储备。然而,《时代》杂志报导说:从开会的工商业者那里,总统的保证得到了一阵掌声。以我们已经声明的政策而言,我们是处在一个入不敷出的人的地位,而这个人又坚持说;他不可能挣得更多或花费得更少,或者借款,或者从他的资产中取得入不敷出的差额!
由于我们一直不愿意采用任何一种连贯性的政策,我们和我们的贸易伙伴——他们象我们一样作同样的鸵鸟般的声明——被迫使用所有的四个机制。在战后年代的早期,美国储备上升;最近,它们一直在下降。与储备上升这一情况相比,我们更乐意于欢迎通货膨胀。由于黄金外流,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通货收缩的程度要比没有黄金外流时为大。虽然我们没有改变我们的黄金的官价,我们的贸易伙伴们却改变了他们的官价,从而也改变了它们的货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在造成这些调整时,美国的压力并不是不存在的。最后,我们的贸易伙伴广泛地使用直接控制,而由于是我们而不是他们面临着赤字,我们对国际收支也采取了大范围的直接干预——从减少旅游者能免税带入的外国货的数量——这是细微而有高度象征性的一个步骤——到要求外援开支在美国使用,到要求家属不和海外军人一起生活,到更严格的石油进口的限额。我们也曾不得不降低身分去请求外国政府对加强美国收支平衡采取特殊的措施。
在四个机制中,使用直接控制显然从几乎任何一个观点来看都是最不好的,而且对一个自由社会具有最大的摧毁性。然而由于缺乏任何明确的政策,我们曾逐渐被引入于依赖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控制。我们公开宣传自由贸易的美德,但是,由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无情压力,迫使我们往相反的方向行进,而我们还具有进一步行进的很大的危险。我们可以通过一切可以想象的减少关税的法律。政府可以协商任何次数的关税削减。然而,除非我们采用另一些机制来解决国际收支的赤字,我们不过是用一套贸易的办法来代替另一套办法——实际上,是用一套较坏的来代替一套较好的。关税固然是坏事,而限额和其他直接干预甚至是更坏。象市场价格一样,关税具有非个人的性质,并不牵涉到政府对商业事务的直接干预,限额则很可能要牵涉到分配及其他行政的干预,此外还给与行政官员一笔有价值的权势作为私人利益走后门之用。或许比关税或限额更坏的是在法律之外的安排,例如日本“自愿”限制纺织品的出口的协定。
作为自由市场解决办法的浮动汇率
只有两种机制是与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相一致的。一个是完全自动调节的国际金本位。正如我们在前一章里看到的那样,这既行不通,又不是理想的办法。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能自己单独采用它。另一个是没有政府干预而完全由市场上的私人交易所决定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是相当于前一章所主张的货币规章的办法。假使我们不采用它,我们将无法扩展自由贸易的范围,并且迟早会不得不对贸易施加广泛的直接控制。在这个领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条件能够并且确实出现意料之外的变化。或许就在写作本书的时候(1962年4月),我们能够糊里糊涂地走出困境,并且可能处于具有盈余而不是处于赤字的状态,累积了而不是损失了储备。果然如此的话,这将不过意味着:其他国家会面临着施加控制的必要性。当我在1950年写论文建议浮动汇率的制度时,当时的前提是伴随着所谓“美元短缺”的欧洲在国际收支上的困难处境。这种变化总是可能的。事实上,很难预料这些变化在何时和如何发生正是赞成自由市场的基本论点。我们的问题不是“解决”一个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我们是要通过采用一种机制来解决整个收支平衡问题,而这种机制又能使自由市场的力量对影响国际贸易的条件的变化,提供一个迅速、有效而自动的反应。
虽然自由浮动汇率看来显然是适当的自由市场机制,但是,强烈地支持它的仅仅是一小部分的自由主义者,其中大多数为职业经济学者,而反对它的却是在几乎所有其他领域中否定政府干预和政府决定价格的许多自由主义者。为什么是如此呢?一个理由单纯是沉溺于现状。第二个理由是真正和虚假金本位之间的混淆。在真正的金本位下,不同国家的货币的相互之间的比价几乎是固定不变的,因为,不同的货币只是不同数量黄金的不同名称。我们很容易错误地认为仅仅采用名义上以黄金为基础的形式便能够实现真正金本位的实质——即:采用虚假的金本位,在其中,不同国家的货币比价的固定不变仅仅因为它们是在市场中受到维持的规定价格。第三个理由是每个人的不可避免的倾向,认为其他人应该使用自由市场,而自己则需要特殊的处理。这在汇率上对银行家特别有吸引力。他们喜欢有一个保证不变的价格。此外,他们对市场会出现的应付汇率的波动的办法并不熟悉。专门在外汇的自由市场上从事投机和套汇的公司并不存在。这是强行维持现状的一种方式。例如,在加拿大,处于十年的自由汇率这一不同现状之后,某些银行家站在赞成继续使用自由汇率的前列并且反对维持固定比价,也反对政府对汇率的操纵。
我相信,比这些理由更为重要的是对浮动汇率的经验作出错误的解释,来源于可以用一个典型的例子加以说明的统计学方面的错误。亚利桑那显然是美国患结核病者能进入的最坏的地方,因为亚利桑那结核病患者的死亡率比任何其他州都要高。在这个例子中,荒谬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关于外汇率,荒谬之处并不如此明显。当国家由于内部货币处理不当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时,它们最后总是不得不采用可以伸缩的汇率。没有任何程度的外汇控制或直接的贸易限制能使它们把汇率维持在脱离经济现实很远的水平。结果,浮动汇率确实是无疑地与财政和经济的不稳定状态频繁地联系在一起——例如,正象在许多南美国家发生的超级通货膨胀的情况那样,或者是严重的但还不是超级通货膨胀的情况那样。我们正和许多人一样,很容易得出浮动汇率造成了这种不稳定的状态的结论。
赞成浮动汇率并不意味着赞成不稳定的汇率。当我们支持国内的自由价格制度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成价格上下剧烈波动的制度。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价格可以自由波动,但是决定它们的因素稳定到足够的程度,从而在事实上价格的运动会处于适当的范围之内。这也同样适用于浮动汇率的制度。最后的目标是达到这样一个状态,在其中,价格虽然可以自由变动,但在事实上,汇率却是非常稳定的,因为基本的经济政策和条件是稳定的,汇率的不稳定是根本的经济结构不稳定的征兆。通过行政办法冻结汇率来消除这个征兆并不能治疗根本的困难,而只能更加痛苦地对困难作出调整。
为黄金和外汇的自由市场所需要的政策措施
如果我详细说明我认为美国为了形成一个黄金和外汇的自由市场所应采取的措施,那末,这会有助于以具体的办法表明目前的论述的含义。
1.美国应该宣布:它不再按固定价格买卖黄金。
2.规定个人拥有黄金或买卖黄金是不合法的目前法律应该废止,从而,对按照任何其他商品或包括国家货币在内的金融票据来买卖黄金的价格就会没有限制。
3.规定联邦储备系统必须拥有等于它债务数额的25%的黄金证券的目前法律应该废止。
4.象完全取消小麦价格维持方案一样,在完全取消黄金价格维持方案中的传统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政府累积下来的存货。在两种情况中,我个人的观点是:政府应该立即执行上述第一和第二点,从而恢复自由市场,并且最后应该出清它的所有的存货。然而,理想的办法很可能是:政府逐渐地出清它的存货。以小麦而言,在我看来五年似乎是足够长的一段时期,所以我赞成政府在五年的每年中出清掉它存货的五分之一。这样长的时期看来对黄金也同样是相当合适的。因而,我建议政府在五年期间在自由市场上拍卖掉它的黄金存货。有了自由黄金市场,个人很可能会认为黄金的库存收据比真正的黄金更为有用。但是,果然如此,私人企业肯定能提供储存黄金的地方并且发给收据。为什么储藏黄金和发给收据应该是国有化的企业呢?
5.美国也应该宣布;它不会规定美元和其他货币之间的官价汇率;此外,它不会从事于目的在于影响汇率的任何投机或其他活动。汇率会在自由市场里决定。
6.这些措施会和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成员来规定美元官方平价这一正式职责发生矛盾。然而,基金组织认为:虽然加拿大没有规定它的货币比价,但它并不和基金组织的条文相冲突,从而,批准加拿大的浮动汇率。没有理由认为它对美国不能同样对待。
7.其他国家可能要维持它们自己的货币和美元之间固定比价。这是它们自己的事,而只要我们不去承担按固定价格购买它们的货币的义务,我们没有理由加以反对。只有使用上述一种或多种手段,他们才能成功地维持它们和我们货币之间的比价——减少或增加储备、使他们的国内政策与美国政策相协调、加紧或放松对贸易的直接控制。
排除美国对贸易的限制
类似上面加以概括的制度将彻底地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不可能出现赤字,而这些赤字需要高级政府官员恳求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支援,或需要美国总统的行动象一个惶恐的小银行的主人那样,设法恢复对他银行的信心,或迫使宣传自由贸易的政府对进口施加限制,或为了微不足道的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而牺牲重要的国家和个人的利益。支付总是平衡的,因为一种价格——外汇率——会不受约束地造成平衡。谁也不能出售美元,除非他能找到购买它们的人,同样的话也适用于相反的情况。
因此,浮动汇率制度能使我们有效地和直接地走向物品和劳务的完全自由的贸易——除了以严格地政治和军事的理由来进行干预的情况以外;例如,禁止出售战略物资给共产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坚持使用固定汇率的紧身内衣,我们不可能肯定地走向自由贸易。作为一种必要时的安全手段,必须保留使用关税或直接控制的可能性。
浮动汇率制度有附带的好处,它几乎能赤裸裸地揭露出反对自由贸易的最流行的论点中的荒谬之处。该论点为:别处的“低”工资使关税多多少少成为必要的事情来保护这里的“高”工资。日本工人每小时得到100日元和美国工人每小时4美元相比是高还是低呢?那完全取决于汇率。什么决定汇率呢?使国际收支平衡的必要,也就是说,使我们能出售给日本人的数量大体上等于他们能出售给我们的数量。
为了简单化起见,设想日本和美国是唯一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同时设想按照某种汇率,譬如说1000日元换一美元,日本能以比美国便宜的办法生产进入外贸的每一样东西。按照这个汇率,日本能出售给我们很多东西,而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出售给他们。设想我们用美元纸币支付他们。那些日本出口商将怎么处理这些美元呢?他们不能吃它们,穿它们或住在美元里面。假使他们只是愿意持有它们,那末,印刷工业——印刷美元票据——将会是一项宏伟的出口行业。它的产量会使我们所有人具有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几乎完全由日本人免费供应。
但是,日本出口商当然不想持有这些纸币。他们想出售它们换取日元。但是,根据假设,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东西全可以用少于1000日元的代价而能购买到,而我们又假设每一美元可以换到1000日元。这对其他日本人来说,也是如此。然而,为什么任何持有日元的人会放弃1000日元来换取一美元,而一美元又要比1000日元买到更少的物品呢?没有人愿意这样做。为了使日本出口商能把他的美元换成日元,他不得不要求少拿几块日元——即:以日元表示的美元价格势必少于1000日元,或以美元表示的日元价格稍多于一美元。但是,按照一美元换500日元之比,那末,日本货对美国人来说要比以往贵一倍,而美国货对日本人来说要便宜一半。日本人就不再可能以较廉的价格向美国出售一切的物品。
以美元表示的日元价格最终会停留在哪一水平呢?最终会停留于能保证一切日本出口商所愿意出售的从出口货换来的美元的数量等于进口商愿意购买的用于进口美国货的美元的数量这一水平。在较松散的意义上说,停留于能保证美国出口货的价值(以美元计)等于美国进口货的价值(也以美元计)。仅在松散的意义上是如此,因为,精确的说法应把资本交易、礼品等等考虑在内。但是,这些并不能改变基本的原理。
可以看到,上面的论述并没有提到日本工人或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这些是与题无关的。假使日本工人的生活水平比美国工人为低,那是由于他在既定的训练水平、既定的资本和土地等的数量之下,比美国工人平均说来具有较低的生产能力。譬如说,假使美国工人平均生产能力是日本工人的四倍,那末,用他来生产少于四倍生产能力的任何物品是一种浪费。较好的办法是:生产那些他的生产能力较高的物品,并且用那些物品来换取他生产能力较低的物品。关税并不帮助日本工人提高他的生活水平或保护美国工人的高的生活水平。相反地,它们降低了日本工人的生活水平,并使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不能达到它应有的高水平。
假使我们都同意,应该把自由贸易作为目标,我们应该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我们一向试图采用的方法是与其他国家相互协商,以使减少关税。以我看来,这是错误的办法。首先,它的步调保证是缓慢的。行动最快的人是单独行动的人。第二,它助长了对基本问题的一个错误的观点。它使人们看到,好象关税有利于施加关税的国家,但却对其他国家有害。好象当我们减少关税时,我们放弃了一些好的东西,从而,应该得到其他国家的关税的降低作为某种报酬。事实上,情况是很不相同的。我们的关税有害于我们自己,也有害于其他国家。即使其他国家不这样做,取消我们的关税会使我们受益。假使他们减少他们的关税,我们当然会受益更多。但是,我们得益并不取决于他们减少他们的关税。各自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不发生矛盾。
我认为,如果我们单方面走向自由贸易,象十九世纪英国废除谷物法那样,结果会好得多。正象他们所做的那样,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会大大地增加。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不应该在减少卢森堡产品关税以前,要求卢森堡采取互利的行动,或者对从香港进口的纺织品施加限额,从而使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失业。让我们担负起我们的历史任务,走在前面,而不做一个勉强的追随者。 为了简单化起见,我的论述仅就关税而言,但是,正象早已看到的那样,非关税的限制现在可能构成一个比关税还要严重的对贸易的障碍。二者我们都应该加以消除。一个迅速而又是逐步的方案为:通过立法使不管是我们制订的、还是其他国家“自愿”接受的进口限额或其他数量的限制每年提高20%,直到它们如此之高,以致成为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从而,可以被放弃掉,同时使所有的关税在今后的十年中减少目前水平的十分之一。
我们还可以采取更好地促进国内外的自由事业的几个措施。我们不应该以经济援助的名义把款项赠送给外国政府——因而促进社会主义——而在同时对他们能生产的产品加以限制——因而妨碍自由企业。我们应该采取一致的和有原则的姿态。我们可以对世界其他地区说:我们相信自由并且企图这样做。谁也不能迫使你取得自由,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是,我们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向你提供完全的合作。我们的市场向你们开放。在这里,你可以出售你能出售和愿意出售的东西,使用售货款来购买你愿意买的东西。以这种方式,个人之间的合作可以遍及全世界而同时又是自由的。
第五章财政政策
自从新政以来,在联邦一级扩大政府活动的主要借口是所谓政府支出在消除失业上的必要性。这个借口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需要政府支出来“开动唧筒”。暂时性的开支能使推动经济制度自行前进;这时,政府便退出这个局面。
当最初的开支不能消除失业,而伴随而来的是1937-1938年的剧烈的经济收缩时,“长期停滞”的理论就发展出来为永久性的高水平的政府开支进行辩护。人们争辩道:经济制度已经成熟。投资的机会已经大部分加以利用,从而,许多新机会的出现不大可能。然而,个人仍然会想要储蓄。因此,政府有必要花费金钱并且造成永远存在的赤字。为了补偿赤字而发行的有价证券会给个人提供积累储蓄的一个办法,而政府的开支则提供就业机会。这种观点已为理论分析所否定,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为实际经验所否定,包括经济长期停滞论者梦想不到的整个新的系列的私人投资机会的出现。然而,它留下了它的影响。可能没有人接受它的观点,但是,以这个观点的名义从事的政府方案,如意图“开动唧筒”的那些方案,目前仍然存在,并且构成不断增长的政府开支的原因。
最近,所强调的方面不是使用政府的开支来开动唧筒,也不是阻止长期萧条的幽灵,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平衡器。据说,当私人开支由于某种原因下降时,政府开支应该上升,以便使整个开支稳定不变;相反,当私人开支上升时,政府开支应该下降。不幸地是,这个平衡器本身就是不平衡的。不管衰退的程度多么微小,每次衰退使政治上敏感的议员们和行政官员们不寒而慄,总是在懼怕着1929—1933年大萧条的征兆的出现。他们匆忙地制定种种联邦支出方案。事实上,许多方案直到衰退过后才开始执行。因而,就它们确实影响整个开支的大小而言,它们倾向于使随之而出现的扩展恶化,而不是使衰退得以缓和。批准支出方案的匆忙程度并不等于当衰退已经过去和扩展开始进行时的撤销或消除它们的匆忙程度。恰恰相反,那时又要提出一个论点,认为“健全的”扩展不应该由于政府开支的削减而受到“危害”。因此,平衡器的原理的主要危害不在于它一向未能做到的抵消衰退,不在于它经常做到的把通货膨胀的倾向带入政府政策,而在于它继续不断地扩大联邦一级政府活动的范围,并且使联邦赋税的负担不能减少。
由于强调使用联邦预算作为一个平衡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战后时期,国民收入最不稳定的组成部分是联邦政府开支,而这个不稳定的开支根本没有处于抵消其他开支的变动的方向。远不是抵消波动的其他因素的平衡器,联邦预算本身的特点就是扰动和不稳定的主要泉源。
由于它的开支在整个经济中现在占有如此庞大的一个部分,联邦政府不能不对经济制度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首先应要求政府修补自己的围墙,即:政府采取使自己的开支具有合理的稳定性的步骤。假使政府能这样做,那末,它显然会有助于减少经济制度中其他领域所需要的调整。除非它能做到这一点,政府官员装出自以为正确的校长教训不守秩序的学生的腔调不过是一出滑稽戏。当然,他们这样做并不值得奇怪,推卸责任和转嫁过失并不单单是政府官员所垄断的坏事。
即使我们接受联邦预算应该和能够用作为平衡器之用这个观点——即:我将在下面较详细地加以考虑的观点——也没有必要为此而使用预算的开支一方。税收的一方是同样可以采用的。国民收入的下降以较大的比例自动减少了联邦政府的赋税收入,从而,趋于使预算具有赤字,而在繁荣时期情况恰好相反。假使希望有较大的变动幅度,那在衰退时期可以降低税收,而在扩展时期提高税收。当然,政治方面的考虑很可能也在这里形成不对称的现象,使得下降比提高在政治上比较令人喜爱。
如果说平衡器原理实际上被应用在开支一方,那末,这是因为趋于增加政府开支的其他因素的存在;特别是知识分子广泛地接受这种信念,认为政府应该在经济和私人事务中起较大的作用;也就是福利国家的哲学的胜利。这种哲学在平衡器原理方面找到了实际应用的伙伴;它使政府干预的步伐比没有它时所可能有的步伐更快。
假使平衡器的原理被应用在赋税一方而不是开支一方,现在的情况可能是多么不同。设想每次衰退都减税一次,又设想在相继发生的扩展的情况下,提高赋税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导致了对新近提出的政府开支方案的抵制和对目前存在的开支方案的削减。我们现在可能处于联邦开支在国民收入占有远为小的部分的地位,而国民收入又会由于赋税对经济发展的抑制和阻止的影响的减少而具有较大的数值。我要立即指出,这个梦想并不表示我对平衡器原理的支持。实际上,即使影响系按照平衡器原理所预期的方面发展,影响在时间和范围上会被推迟。为了使它们有效地来抵消造成波动的其他因素,我们势必要在很长时期以前能够预测到那些波动。在财政政策以及在货币政策中,即使我们抛开一切政治因素,我们的知识还不足以使我们能运用随意变动的税收或开支,把它们当作为灵敏的稳定机制。在试图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几乎肯定会使事情变得更坏。我们之所以使事情变得更坏并不在于一贯使用错误办法——那是很容易纠正的,只要我们去做与开始看来要做的相反的事情。我们之所以使事情变为更坏是由于引进了一个可以单纯加在其他干扰之上的主要为随机变动的干扰。事实上,那似乎就是我们在过去所做过的事情——,此外,当然还有严重的错误之处。我在别处写的有关货币政策的东西同样可以适用于财政政策:“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对路线的意想不到的曲折能熟练地不停转动经济车轮的方向盘的货币驾驶员,而是需要一些措施,使得坐在后座作为压舱物的货币乘客不致偶然地把身体向前倾斜并且猛转一下方向盘,以致可能使车辆脱离大道。”
对财政政策而言,相应于货币方面的规章是:完全根据整个社会需要通过政府而不是通过私人所要做的事情来计划开支方案,而丝毫不考虑逐年的经济稳定问题,来率先规定税率以便得到足够的收入,用以大致补偿有关年份的计划开支,同样也不要考虑逐年的经济稳定问题;以及来避免政府开支或赋税的突然变化。当然,某些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国际形势的突然变化可以造成军事开支的大量增加或造成人们所欢迎的军事开支的减少。这些变化可以说明战后时期联邦开支的某些突然的变化。但是,它们决不能说明全部变化。
在离开财政政策这个主题之前,我想论述一下目前人们广泛持有的观点,认为:相对于税收数量而言,政府开支的增加必然是扩张性的,而政府开支的减少必然是收缩性的。这个观点的核心是相信财政政策可以被用作为平衡器。它在目前几乎已经被商人,专业经济学者以及一般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它不能被逻辑上的考虑单独证明是正确的;它也从未被经验所证实。在事实上,它还是和我所知道的有关的实际资料不相一致。
这个信念的根源是粗略的凯恩斯主义的分析。设想政府的开支上升100美元,而赋税保持不变。于是,思想简单的分析的想法是:在第一个回合,得到新增加的100美元的人们等于得到了一笔同样多的收入。他们会储蓄其中的一部分,譬如说储蓄了三分之一,而花掉剩下的三分之二。但是,这意味着,在第二个回合,另外有人得到额外的66又2/3美元的收入。他依次又储蓄一些并且花掉一些,如此等等按次无限地进行下去。假使在每一个回合,储蓄为三分之一,花费为三分之二,那末,根据上述分析,额外的100美元的政府开支最后将使收入增加300美元。这是简单的凯恩斯主义的乘数分析,其乘数为3,当然,假使注入于经济制度中的货币仅为一次,效果将会消失,100美元的收入的最初的增加会逐渐下降到原有的水平。但是,假使政府开支的增加保持在每一单位时间100 美元,譬如说一年的增加为100美元,那末,根据上述分析,收入会停留于比过去高300 美元的水平。
这种简单分析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这种吸引力是虚假的,并且是由于忽视了上述变化的其他有关影响而造成。当对这些因素加以考虑时,最后的结果就使人更加怀疑;结果可能是从收入一点没有变化到变化了上述全部规定的数量;而在收入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政府开支增加100美元使私人开支减少100美元。即使货币收入增加,价格可能上升,从而,实际收入增加不多或者根本没有增加。让我们考虑一些露出破绽的地方。
首先,在上面的简单的分析中没有说明政府的100美元花费在什么东西上。例如,设想政府把它花费在私人本来就想购买的东西上。譬如说,政府花100美元于公园门票,而门票收入被用来支付公园的清洁工人。设想政府现在支付这些费用,从而允许人们“免费”进入公园。清洁工人仍然获得相同的收入,但是,原来支付这些费用的人们现在多余了100美元。甚至在这个开始阶段,政府的支出并没有增加任何人的收入。它所做的是让一些人多余了100美元,可以被用于除了公园以外的其他目的,很可能是他们的估价不象公园那样高的目的。他们从收入中花费于消费品上的钱可以被设想为比以前要少,因为他们现在得到免费的公园劳务。究竟少多少是很难断定的。即使我们象在简单的分析中那样接受人们储蓄掉他们增加的收入的三分之一这一论点,那也不能说:当他们得到一批“免费的”消费品时,由此而节约的金钱的三分之二将被花费于其他消费品之上。当然,一个极端的可能性是他们将继续象他们以往那样,来购买同样数量的其他消费品,并且把节约下来的100美元放在他们的储蓄之内。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使用简单的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政府开支的影响完全被抵消掉:政府开支上升100 美元,而私人开支下降100美元。另外再举一个例子,花费100美元来建造私人企业本来也会建造的一条道路,或者,这条道路的建造可以使公司的卡车不需要加以修理。于是,公司会有由此而节约下来的资金,但很可能不会把该资金的全部用于吸引力较道路为少的投资之上。在这个情况中,政府开支只是转移私人开支,而显然只是政府开支超出的净额才能提供被乘数去乘的数值。从这个观点来看,能保证没有转移的办法是使政府把金钱花费在完全无用的东西上——这就是人为地提供就业机会的“填补地上的窟窿”的方式在智慧上的有限内容。然而,这个事例的本身当然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是有些问题的。
其次,在简单的分析中,没有说明政府所花费的100美元来自何处。就这个分析本身而言,不论政府是否印刷额外的货币或从群众那里借款,结果都是一样。但是,可以肯定,它采取哪一种办法是举足轻重的。为了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开,我们假设政府借了100美元,因此,货币数量保持不变,正象在没有政府开支的情况下的货币数量一样。这是一个恰当的假定,因为,在没有额外的政府开支时,货币数量是能够增加的。假使我们有这样做的需要,那末,我们可以印刷货币供用之于购买现有的政府债券。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问:借款的影响是什么。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假定转移并不存在,所以我们首先同意对100美元的政府开支,并不存在私人开支下降这一形式的直接的抵消。应该注意,政府使用借款的方法来增加开支并不改变私人手中的货币量。政府用它的右手从某些个人那儿借来100美元,而在进行开支时,用它的左手把等量的货币交给被支付的那些个人。不同的人们持有货币,但是,所持有的货币总量则是不变的。
简单的凯恩斯主义分析暗地里假设:借用货币对其他的开支项目没有任何影响。在两种极端情祝下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第一,假设人们对于他们是否持有债券或货币完全漠不关心;所以,为了取得 100美元而出售的债券可以在不给买主提供比这些债券以前的利息为高的情况下被卖掉。(当然, 100美元是很小的数量,以致实际上对利息率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里所谈的牵涉到经济学原理,其现实的重要性可以通过把100 美元变为100个百万美元或100个千万美元而看出来。)以凯恩斯主义的名词来说,存在着一个“灵活陷阱”的情况,所以人们用“闲散的货币”来购买债券。假使情况不是这样,而显然不可能无限期地存在着这种情况,那末,政府只能提高债券的利息率才能把它卖掉。那时,其他的借款者也不得不支付较高的利息率。较高的利息率一般会挫伤借款者的私人开支。这里出现简单的凯恩斯主义的分析可以适用的第二种情祝:假使借款者对于开支是如此坚决,以致不论利息率高到什么程度,他们的开支都不会削减。或者,以凯恩斯主义的名词来说,即为投资的边际效率曲线完全缺乏弹性的情况。
据我所知,没有任何成名的经济学者,不管他把自己看作为多大程度的凯恩斯主义者,会把这些极端的情况中的任何一个看作为目前存在的事实,或在借款数量的变动或利息率升高具有相当大幅度的情况下存在的事实,或在过去除了比较特殊的情况下已经存在过的事实。然而,很多经济学者,更不必说非经济学者,不管他是否把自己看作为凯恩斯主义者,都把下面的说法当作为正确的东西接受下来,即:相对于赋税收入的政府开支的增加,即使其资金来自借贷,也必然具有扩展经济活动的性质,尽管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说法以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中的一个为前提。
假使上述假设条件没有一个能够成立,政府开支的增加将为私人开支的下降所抵消,因为,借款给政府的人或本来想要借款的人的支出要下降。多大的开支增加会被抵消掉呢?这取决于货币持有者。严格的货币数量论所包含的极端情况的假设条件是:人们想持有的货币量,平均说来,只是取决于他们的收入,而不取决于他们在债券或类似的有价证券上能获得的利息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货币总量在事前和事后均是一样,为了使人们正好满足于持有不变的货币总量,整个货币收入也必须相同。这意味着利息率不得不上升到足够的程度,以使减少私人开支数量,使减少的数量正好等于政府开支的增加。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政府开支是扩展性的说法是毫无意义的。甚至货币收入也没有上升,更不用说真正的收入了。发生的全部事实是:政府开支上升,而私人开支下降。
我提醒读者,这是一个高度简单化的分析。一个全面的分析需要一本篇幅很长的教科书。但是,即使这样简单的分析也足以证明300美元和0之间的任何数值的收入的增加都是可能的后果。消费者越是坚持在一定的收入中花费掉一定的数量,投资者越是不管成本大小而坚持购买一定量的资本品,则结果越是接近于收入增加300美元的凯恩斯主义的极端。另一方面,货币持有者越是在他们持有的现款和收入之间坚持一定的比例,则结果越是接近于收入的变动为0的严格的货币数量论的极端。公众究竟坚持哪一个方面是一个根据事实来判断的现实问题,而不是单单由理论来决定的东西。
在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前,大部分经济学者无疑地会得出结论,认为结果会接近于收入的上升为0,而不是上升为300美元。自从那时以后,大部分经济学者无可否认地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最近,出现了返回原有观点的动向。令人惋惜的是:在这些观点的变动中,没有一个可以说是以满意的证明为基础的。它们的基础是根据粗略的经验而作出的直觉的判断。
和我的一些学生合作,我曾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做了一些相当广泛的现实资料的研究,以便取得一些比较令人满意的证据。结果是惊人的。它们强烈地表明:实际的结果更接近于货币数量论的极端,而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极端。根据这一研究成果而作出的判断似乎是:所假设的100 美元的政府开支的增加平均说来大致会增加 100美元的收入,有时少些,有时多些。这意味着:相对于收入的政府开支的增加,在任何有关意义上都不是扩展性的。它可以增加货币收入,但是,这一增加均由政府开支所吸收,私人开支则为不变。由于价格在这一过程中很可能要上升或者比没有政府开支增加的情况下降低得少一些,结果使实际的私人开支减少。政府开支的下降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当然,这些结论不能被看作为最后的结论。它们系以我所知道的最广泛和最全面的证明材料为基础,但是,证明材料本身仍然在很多方面需要加以改善。
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显然的,不论如此广泛地被接受的关于财政政策影响的观点是否正确,它们至少和一个内容广泛的证明材料相抵触。我还没有看到任何前后一贯和组织严密的能论证它们的正确性的证明材料。它们是经济神话的一部分,而不是经济分析或数量研究所论证的结论。然而,它们在取得群众的广泛支持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使政府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干预经济生活。
第六章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作用
正规学校教育在今天系由政府机关或非利润的机构提供经费,并且几乎完全由它们所管理。这种形势系通过逐渐的发展而形成,从而,目前人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再把注意力明确地指向学校教育受到特殊对待的理由,甚至在社会组织和指导思想方面均为自由企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也是如此。结果是政府的职责无原则地扩大。
按照第二章所论述的原理,政府对教育具有两个进行干预的理由。第一个是相当多的“邻近影响”的存在,即:一个人的行动迫使其他人为之支付相当大的代价,而又无法使前者赔偿后者的情况,或者,个人的行动对其他人产生相当大的好处,而又无法使后者赔偿前者的情况——即:使自愿交易成为不可能的情况。第二个是对孩子们和其他对自己行动不负责任的个人的家长主义的关怀。对(1)公民的一般教育和(2)专业的职业教育,邻近影响和家长主义关怀具有非常不同的含意。在这两个领域内政府于预的理由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之处,而且所应采取的行动的类别也是非常不相同的。
还有一个在开始时需要加以说明之点:把“学校教育”和“教育”区别开来是重要的。并不是所有的学校教育都是教育,也不是所有的教育都是学校教育。我们所关心的主题应该是教育。政府的活动则主要以学校教育为限。
公民的一般教育
如果大多数公民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文化和知识,也不广泛地接受一些共同的价值准则,稳定而民主的社会不可能存在。教育对文化知识和价值准则这两个方面,均会作出贡献。结果,儿童受到的教育不仅有利于儿童自己或者家长,而且社会上其他成员也会从中得到好处。我的孩子受到的教育由于能促进一个稳定和民主的社会而有助于你的福利。由于无法识别受到利益的具体的个人(或家庭),所以不能向他们索取劳务的报酬。因此,存在着相当大的“邻近影响”。
这种特殊的邻近影响应该引起政府的哪一种行动呢?最显然的是要求每一个儿童受到最低数量的一种特殊的学校教育。这种要求可以施加于家长而不需要政府进一步的行动,正象要求建筑物和汽车的所有者遵照特殊标准以便保护其他人的安全那样。然而,在两种情况之间存在着差异。凡是付不起建筑物或汽车的安全标准的费用的个人一般可以放弃他们的财产而将它出售。因此,这个要求一般能够加以实施而不需要政府的津贴。把孩子和缴纳不起最低要求的学校教育学费的家长分离开来,显然和我们把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办法以及和个人自由的信念不相一致。此外,这很可能不利于自由社会的公民教育。
假使这种学校教育的要求所引起的经济负担能很容易地为社会里的大量家庭所承受,直接要求家长们来承担这笔费用是可行的,也是需要这样做的。极端的情况可以通过向贫穷家庭提供特殊的补贴而得以解决。在今天的美国,很多地区符合于上述条件。在这些地区,把要求的各种费用直接加在家长的身上是应该使用的办法。这可以取消政府的一个机关。这一机关目前在所有居民的一生中向他们征收赋税,然后在他们的孩子上学期间,又把税款的大部分付还给同样的那些人们。这会减少政府同时也管理学校的可能。对此,下面将进一步加以论述。这会使减少津贴在学校经费中的比重更有可能,因为,随着收入的一般水平的增加,对于这种津贴的需要也会随之而下降。假使象现在那样,政府负担全部的或极大部分的学校经费,收入的增加只会使通过赋税机关的款项的流动进一步扩大,从而扩大了政府的作用。最后,但是决不是最不重要的,家长负担孩子的教育费用可以使生育孩子的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相等,从而,也有利于形成一个较好的家庭成员数目的分配。
不同家庭之间的财富和孩子多少的差异,加上维持一定标准的学校教育会引起相当可观的费用,使这种政策在美国许多地区难于实行。在这些地区以及在这种政策可实行的地区,政府都负担了学校教育的经费。政府所支付的经费不但包括一切人都必须受到的最低限度的学校教育,而且也包括年轻人受到的、但却不是必要的较高水平的学校教育。论证负担两种经费的理由是上面讨论过的“邻近影响”。政府支付费用,因为,这是实施最低水平的学校教育的唯一可以实行的手段。政府负担较高水平的学校教育,因为,其他的人能从有能力和有兴趣的那些人的学校教育中获得好处,那些人可以提供较好的社会和政治领导的水平。从这些措施中获得的好处必须和费用相比较。对于应该给与多大的津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真实的意见的分歧。然而,我们中间大多数人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得到的好处是一个足够重要的因素来决定政府津贴的大小。
这些理由只能论证政府给与某种学校教育的津贴是必要的。可以设想,这些理由并不能论证津贴纯粹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因为,它仅增加学生在经济上的生产能力,而不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或领导能力的教育。要在两种学校教育之间划一条明显的界线是非常困难的。大部分的一般学校教育增加学生的经济价值——确实,仅仅在目前的几个国家中具有文化知识不再具有市场价值。同时,大量的职业教育扩大了学生的视野。然而,对二者加以区别还是很有意义的。象广泛地在美国政府支持的教育机构中所做的那样,对兽医、美容师、牙医以及许多其他专家的训练给与津贴的理由是不能论证对初等学校或对更高水平的文理科综合大学给与津贴的必要性的。是否能以完全不同的理由来论证津贴后者的必要性将在本章较后的部分加以论述。
当然,“邻近影响”在质的方面的论点并不能决定应该津贴什么水平的公民教育或应该津贴多少。可以设想,最低水平的学校教育对社会具有最大的益处。对于这种教育的内容,意见是最接近于一致的。随着学校教育水平的上升,社会得到的利益会持续下降。即使这种说法也不能完全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很多政府在津贴低级学校以前很久就津贴大学。什么形式的教育有最大的社会利益和社会的有限资源的多大部分应花费在它之上,必须取决于通过社会认可的政治渠道所表示的公众的意见。我们的分析的目的不是替社会来决定这些问题,而是澄清在作出决定时所涉及到的问题,特别是作出的决定是否能以社会的而不是以个人的利益为基础。
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国家可以用“邻近影响”为理由来规定最低水平的学校教育以及向它提供经费。第三个步骤,即:政府对教育机构的实际管理,好象是对大部分“教育事业”的“国有化”那样,是非常难以用这些理由加以论证的,而据我看来,也是非常难以用其他理由加以论证的。这种国有化是否有必要的问题很少明确地被提出来。政府向学校教育提供经费的主要办法是直接支持管理教育机关的费用。这样,这一步骤看来似乎与津贴学校教育的决定是分不开的。然而,这两个步骤能很容易地被分开来。为了对政府所规定的最低学校教育提供经费,政府可以发给家长们票证。如果孩子进入“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这些票证就代表每个孩子在每年中所能花费的最大数量的金钱。这样,家长们就能自由地使用这种票证,再加上他们所愿意添增的金额向他们所选择的“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购买教育劳务。教育劳务可以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教育机关或非营利的教育机关所提供。政府的作用限于保证被批准的学校的计划必须维持某些最低标准,很象目前对饭馆的检查,要求保证最低的卫生标准那样。这种方案的一个好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退伍军人的教育方案。每个合格的退伍军人每年发给一笔最大限额的款项,可以被使用于他所选择的能维持某些最低标准的任何教育机关。比较有限性的一个例子是英国的规定:对于进入非公立学校的某些学生,地方当局为他们交付费用。另一个例子是法国的办法:对进入非公立学校的学生,国家支付其一部分费用。
以邻近影响为基础的支持学校国有化的论点是:如果没有国有化,则不可能提供被认为是对社会稳定所必要的共同的价值标准。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对私立学校规定最低水平也许不足以得到这个结果。这个问题可以用不同宗教团体所设立的学校加以具体说明。人们可能进行争辩,认为这些学校将灌输成套的社会价值标准,不但在相互之间发生矛盾,而且也和非教会学校所灌输的发生矛盾。以此而论,它们把教育变成为一个分裂而不是统一的力量。
把这个论点推到极端,它不仅能要求政府管理学校,而且能强迫人们进入这种学校。在美国和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中,目前的安排是折衷的办法。存在着政府管理的学校,但并不是强迫进入的。然而,在为这种学校提供经费和对它的行政管理之间的联系使其他学校处于不利地位:它们在政府给与学校教育的经费上没有获得或很少获得好处——这是一种一直在引起大量政治争论的情况,特别在法国和目前的美国,更是如此。有人担心,消除掉这种劣势会大大增强教会学校的地位,从而使得到共同的价值标准问题成为更加困难的事。虽然这一论点具有说服力,然而,它决不能说明它的正确性,也不能说明取消学校教育国有化会具有它所预期的影响。从原则方面考虑,它和保存自由本身发生冲突。一方面为了社会的稳定,需要公共的社会价值标准。另一方面,灌输思想妨碍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在二者之间画出一条大致的界线是易于说而难于做的事例之一。
就影响而言,消除学校教育国有化将扩大家长可以选择的范围。假使象现在那样,家长能不支出特殊费用而送其子女进入公立学校,那几乎没有人会送其子女去到其他学校,除非这些学校也得到津贴。教会学校由于得不到国家的教育经费而处于不利地位,但是它们的有利之处为:领导它们的机构愿意津贴它们并且可以为此而筹募资金。私立学校很少有其他津贴来源。假使不管家长送其子女到什么学校,目前国家在学校教育上的开支都拨给家长使用,那末,各种类型的学校会大量出现来满足这种需要。家长可以把他们的孩子从一个学校退学而到另一个学校,并且通过这个办法来表示他们对学校教育的意见,其彻底的程度要远大于目前所可能做到的。一般说来,他们现在只在支付相当的代价时才能采取这个步骤——把他们的孩子送往私立学校或迁往别处。除此以外,他们只能通过繁琐的政治渠道来表达他们的意见。或许在政府管理的制度下,选择学校的自由程度可以有所扩大。但是,由于政府有责任为每个孩子提供一个学习位置,所以大量扩大这种自由是会有困难的。在这里,正和在其他领域一样,竞争性的企业可能在满足消费者要求方面比国有化企业或为其他目的而经营的企业远为有效。因此,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教会学校的重要性不是增长,而是下降。
在同一方面的有关因素是:把子女送入教会学校的家长势必不愿意增加赋税以便为公立学校提供较多的经费。结果,在那些教会学校有重要影响的地区,为公立学校筹募经费会有很大的困难。经费会影响教育质量,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毫无疑问的。以此而论,公立学校在这些地区质量较差,而教会学校相对地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认为政府领导学校教育的必要性在于它是一种统一的力量这一论点的另一种特殊说法是:私立学校会加深阶级之间的差别。仅使在选择孩子的学校上给与家长较大的自由,那末,同一类型的家长会作出相同的选择,从而,使不同背景的孩子不能健康地相互混合。不管这个论点在原则上是否正确,我们并不清楚,该论点所说的结果会必然到来。在目前的安排下,不同阶层的人们居于不同的居民区这一事实有效地限制了背景大不相同的孩子们的相互混合。此外,现在并不阻止家长们送他们孩子进入私立学校。除了教会学校以外,只有人数非常有限的阶级才能够并且也在实际上这样做,从而造成了进一步的阶层分化。
在我看来,这个论点似指向几乎完全相反的方向——指向学校的非国有化。你问问自己,低收入居民区的居民,更不用说在一个大城市的黑人区的居民,是在哪一方面最为不利。假使他,譬如说,非常重视一辆新的汽车,他可以通过储蓄而积累足够的金钱来购买和郊区收入高的居民同样的汽车。为了这样做,他不需要迁往郊区。恰恰相反,他可以部分地借助于低收入的地区的住房的便宜来节约出这笔钱。对于衣着、或家具、或书籍、或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但是,假设贫民窟里一个贫穷的家庭里有一个有天才的孩子,而又非常看重孩子的教育,以致愿意为此而节衣缩食地进行储蓄。除非这个家庭能在为数极少的一个私立学校里得到特殊的待遇或得到奖学金的帮助,否则,它会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好的”公立学校位于收入高的居民区。这个家庭可能愿意在赋税以外,为它的孩子的教育再花一些钱。但是要在同时又迁往奢华的居民区是很难负担得起的。
我相信,在这些方面,我们的观点依然受到在一个小城镇里只有一个穷人和富人的孩子都能进去的学校这一情况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公立学校很可能会提供均等的机会。随着市区和郊区的增长,形势已经起了急剧变化。我们目前学校教育制度,远远不是使机会均等,却很可能造成相反的结果。对于才能出众的少数人——他们是将来的希望,目前的教育制度使他们超越原有的贫穷状态的行动变为非常困难。
另一个支持学校国有化的论点是“技术垄断”。在小市镇和乡村地区,儿童的数目很少,以致没有理由成立一个以上的有一定规模的学校,因此,不能依靠竞争来保护家长和儿童们的利益。象技术垄断的其他情况一样,可采取的代替方法是不受限制的私人垄断、国家控制的私人垄断和国家经营——在这些坏的事物中,选择坏处较少的一个。这种议论,虽然显然是正确的和重要的,但在近几十年间由于交通运输的改善和人口急剧地集中于城市而大为削弱。
根据这些考虑而作出的近乎显合理的安排——至少对初等和中等教育而言——是公立和私立学校的联合。凡选送孩子进私立学校的家长将得到一笔款项,相当于在公立学校培养孩子的估计费用,如果这笔款项是为了孩子的教育用于被批准的学校的话。这种安然可能满足“技术垄断”论点的正确部分的要求。它将解决家长们正当的抱怨,即:假使他们送孩子去私立的、没有津贴的学校,他们就等于支付两次教育费用,一次系以一般税收的形式,一次是直接支付学费。它将使竞争得到发展。这样,也能推动所有学校的发展和改善。把竞争引进来会大大刺激学校类型的多样化的健康发展。它也将有助于把灵活性带入学校制度。它的相当有利之处,还在于使学校教师的工资能够反映市场的作用。因此,它将给国家当局一种判断工资尺度的独立标准,并且促进更迅速的调整来反映供求情况的变化。
目前被广泛地提出的意见是:学校教育大量需要的是金钱,因为,它可以被用来建造较多的设备,也可以为了招聘更好的老师而给老师以较高的工资。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诊断。花费在学校教育上的钱数一直以异常高的比例上升,比我们总的收入上升要快得多。教师的工资一直要比类似的职业的利润以快得多的速度上升。问题主要并不在于我们花钱太少——虽则我们可能如此——而是我们从每花一美元中所获得的太少。或许在好多学校中花费在雄伟的建筑和奢侈的场地上的钱数被正式地划归为学校教育的开支。把它们作为等同于教育开支的项目是难于接受的。把编织篮子、社交舞蹈和为数众多的其他特殊项目的课程算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贡献也同样是难于接受的。我要立即指出:假使家长愿意的话,他们把自己的钱花费在这种浮华的项目之上并不会引起人们的反对,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反对的是把同样加在家长或者非家长身上的来自赋税款项用于这些项目之上。在这些项目中,“邻近影响”又在哪里呢?
这种使用公款方式的主要原因是目前的把学校的行政和它们的经费来源合排起来的制度。愿意看到款项用于更好的老师和更好的教科书,而不用于体育教练和房屋走廊的家长没有办法来表示这种意愿,除非通过说服大多数人来改变这种对大家说来都是相同的使用款项的方式,这是市场允许每个人来满足他自己的偏好这个一般性原理——即;有效的按比例的表达意见的方式——的特殊事例,而政治方式则把一致性强加于所有的人。另外,喜欢在他孩子教育方面额外花钱的家长受到很大的限制。他不能在他孩子目前消耗的教育经费上增加一些金额,并把他的孩子转送到一个费用较高的相应的学校。假使他一定要让他孩子转学,他必须缴付整个费用,而不仅仅是额外的费用。他只能很容易地花费额外的费用于课外活动——私人舞蹈指导,私人音乐指导等等。由于私人在学校教育方面花费更多金钱的方式受到如此的限制,在儿童教育方面花费更多金钱的压力表现为越来越多的教育经费被花费于越来越多的项目之上,而这些项目和政府干预学校教育的本旨的距离又越来越远。
正象这个分析所暗示的,采用我们建议的安排可能意味着较小的政府在学校教育上的开支,而学校教育的整个费用则较高。这会使家长们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从而使他们花费的金钱大于目前直接花费的和通过赋税而间接花费的数量。它将使家长们免于在孩子的教育上花费更多金钱的愿望受到挫折,因为,在目前,必须服从教育经费的使用方式;同时,目前没有孩子在学校读书的家长势必不愿意增加自己的赋税负担,特别是那些在将来也不会有孩子在学校读书的那些人,更是如此。况且在他们看来,教育经费又往往花费于远离教育的项目。
关于教师们的工资,主要问题不是工资的平均水平太低——平均水平也很可能太高——而是工资过于一致和固着不变。不好的教师报酬过高,而好的教师报酬太低。工资级别趋向于一致,并且主要取决于资历、获得的学位以及得到的教学证书,而不是工作成绩。这主要地也是目前政府管理学校制度的一个后果,而随着被政府管理的单位的扩大而变为更加严重。这一事实本身正是为什么专业教育组织如此强烈地赞成扩大这个单位的一个主要原因——从地方的学校区到州,从州到联邦政府。在任何官僚的、主要为文官制度的机构中,固定的工资级别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几乎不可能来仿效竞争的模式,使得按照工作成绩来决定的薪金具有很大的差别。教育工作者,即:老师他们自己,逐渐取得首要的控制。家长或地方集体逐渐取得少量的控制。在任何领域中,不管它是木工、管子工还是教工,大多数的工人赞成固定的工资级别,而反对按照工作成绩而给予不同的工资;其明显的原因在于有特殊才能的人总是很少。这是一般倾向的一个特殊事例;而这个一般倾向的内容是:不论通过工会或是行业的垄断,人们企图勾结在一起以便决定价格。但是,相互勾结的协定一般会被竞争所破坏,除非政府强制执行它们,或至少给它们一定的支持。
假使有人想要故意设计一种招聘和酬劳教员的制度,目的在于排斥有想象力的、大胆的和自信的人,而又吸引愚蠢的、平庸的和缺乏灵感的人。他应使用的几乎为最好的办法便是仿效在大城市中和在整个州中存在的要求教学证书和执行固定工资级别的制度。或许令人吃惊的是初等或中等学校的教学能力水平处于这种制度所能容许的那种最高状态。选择另一种制度会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允许竞争来发生作用,以便能按照工作成绩给予报酬和把有能力的人吸引进来。
为什么在美国政府干预学校教育沿着它过去的路线发展呢?我没有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教育史方面的具体知识。然而,作出几个猜测可能有利于说明可能改变社会政策的各种考虑之点。我并不肯定:我现在建议的安排方式在一个世纪以前是否合乎要求。在交通运输广泛地被建立起来以前,“技术垄断”的论点远为适用。同样重要的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的主要问题不是促进多样化,而是创造一个稳定社会所必要的共同的社会价值的标准。巨大的移民的洪流从全世界各地涌入美国;移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和遵守不同的风俗。美国这一“人的熔炉”不得不开始使用一些造成一致性的措施和使人们忠诚于共同的价值的措施。公立学校在完成这个任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至少得把英语作为共同语言。在另一种发给票证的方案下,加在有待于批准的学校的最低标准可以包括英语的使用。但是在一个私立学校的制度中,要保证对上述的要求能得到满意的执行,困难可能是很大的。我并不想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公立学校制度肯定比另一种代替的制度较为可取,而只是说,公立学校在那时比现在可能具有远为充分的必要性。我们在今天的问题不是强使人们一致,而是我们受到过多的一致性的威胁。我们的问题是扶植多样化,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另一种代替的制度会比公立学校制度更为有效得多。
一世纪前可能很重要的是另一个混合因素,即:人们对接受发给的现金(“施舍物”)的耻辱心情以及缺乏一个有效的行政机器来发给票证并且检查票证的使用。这种机器是目前时代的现象,随着个人赋税和社会保险的广泛的扩大而达到很大的规模。由于没有这种机器,对学校的管理可能在过去被看作为提供教育经费的唯一可能方法。
正如上面引用的一些例子(英国和法国)所表明的那样,我们所建议安排的某些项目存在于目前教育制度之中。我相信,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里,存在着强有力的和日益增长的压力来实现这种安排;其部分原因在于:现代政府行政机构的发展为这种安排提供了方便的条件。
虽然从目前的转换到我们所建议的制度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行政问题,这些问题似乎不是不可能解决的,也不是为这一过程所独有的。正如在其他活动的非国有化时那样,既有的房屋和设备能卖给想进入这一个领域的私人企业。因此,在这种过渡中不会有物质设备的浪费。由于至少在某些范围内,政府的机构会继续管理学校,这种转换会是逐渐和容易进行的。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里,地方的教育行政机关将同样地助长这种过渡,因为它将鼓励小规模的试验。在决定是否能从某一具体政府单位获得补助金的问题上无疑地会出现困难,但是,这与决定哪一个单位有义务为一个具体儿童提供学校教育的现有问题上是相同的。补助的金额的不同会使一个地区比另一个地区更有吸引力,正象目前学校教育的质量上的差异具有同样的影响一样。唯一额外的复杂之点是可能有更多滥用职权的机会,因为有更大的自由来决定儿童接受教育的学校。假设行政上的困难是反对任何与现状不同的建议的典型理由,那末在我们的这个特殊情况下,这一反对的理由要比在通常情况下甚至更加软弱无力;因为,目前的安排方式不但要碰到所建议的安排方式引起的主要问题,而且还要碰到把管理学校当作为政府职能之一所引起的其它问题。
学院和大学水平的学校教育
前面的论述主要关系到初等和中等学校教育。对高等学校教育而言,以邻近影响或以技术垄断为理由的国有化甚至是更为软弱无力。就学校教育的最低水平而言,对于民主社会的公民教育的应有的内容——阅读、书写和计算占有其中的大部分,存在着相当一致的意见,几乎接近于完全同意。随着水平的持续提高,同意的程度愈来愈少。当然,远在美国大学教育之下,意见一致的程度已经少到不能用多数人的观点来代表全体的观点,更不用说,以多于多数人的观点来代表全体了。确实,缺乏一致的意见可能扩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使人甚至怀疑向处于这个水平的学校提供补助是否恰当。缺乏一致的意见当然大到足够的程度使得以提供共同的社会价值标准为理由的学校国有化受到妨碍。
有鉴于个人为了进入高等学府而可能并且在实际上旅行的距离,在大学教育水平,几乎不存在“技术垄断”的问题。政府机构在美国高等教育方面比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起的作用较少。然而,它们的重要性却大大增加;直到二十年代肯定如此,而现在则占有进入大专院校的学生的一半以上。它们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的价格相对低廉;大多数州立和市立的大专院校的学费远低于私立大学不得不征收的数量。由于这个缘故,私立大学有着严重的财政问题,并且相当有理由地埋怨“不公道”的竞争。它们想保持脱离政府的独立性,而同时又由于财政上的压力被迫去寻找政府的援助。
前面的分析提供了一条能找到圆满解决问题的途径。用于高等教育的公共开支的辩解理由是:为了培养年青人成为公民和社会领袖——虽然我要很快追加一句:目前占有很大比重的用于纯粹职业训练的开支不能使用这种辩护的理由,或者,确实象我们将看到那样,没有任何辩护理由。把对学校教育的补助限制于公文学校的范围是不能以任何理由来为之辩护的。任何补助应该给与个人,用之于他自己所选择的机构,只要这种学校教育是值得给与补助的。任何保留下来的公立学校应该收取能偿付其成本的学费,从而,能在同一水平和私立学校相竞争。除了资金应该来自州而不是联邦政府以外,结果所得到的补助学校教育的办法大致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向退伍军人提供教育费用所采取的安排。
采用这些安排会有助于使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进行更有效的竞争,以及使它们更有效地使用它们的资源。它会消除要求政府对私立高等学校直接援助的压力,从而,能保持它们完全的独立性和多样化,而与此同时又能使它们作出相对于公立学校的成长。它的附带的有利之处是:可能考查到补助的使用是否符合给与补助的目的。对学校而不是对个人给与补助导致了不加区别地补助学校的所有活动,而不是补助国家应该补助的活动。甚至于粗略的考查也可以说明,虽然两种活动有相互重叠之处,但它们远远不是等同的。
认为我们提出的安排方式是公平合理的这一论点在高等教育水平特别容易看得清楚,因为,目前存在着大量的各种私立学校。例如,俄亥俄州对它的公民们说:“假使你有年轻人要进入大学,假使他或她能满足相当少的受教育的条件,而又假使他或她能干到选择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地步,我们将自动地给他或她一笔相当数量的四年奖学金。假使你的年轻人想去,或你要他或她去奥伯林学院或西部准备大学,更不必说,去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西北大学、伯洛伊特大学或芝加哥大学,我们连一分钱也不给他。”这样一个方案怎么能说得过去呢?如果俄亥俄州把它所愿意花费在高等教育的钱用之于任何大专院校读书都能得到的奖学金,而同时要求俄亥俄州立大学在同一水平和其他大专院校相竞争。这样做不是比较公平合理,不是比较有利于提高学术水平吗?
职业和专业学校教育
职业和专业学校教育没有上述的被认为是一般教育所具有的那种邻近影响。它是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一个方式,类似对机器、建筑物或者对其他形式的非人类资本进行的投资。它的功能是提高人类在经济上的生产力。假使一个人这样做,他在一个自由企业的社会中将为了他提供的劳务而获得比他不这样做时所能得到的要高的报酬。这种收益的差别便是进行资本投资的动机,不论以投资于机器,还是投资于人力而论,都是如此。在两种情况下,额外的报酬必须与获得额外报酬的费用相对比。对职业教育而言,主要的费用是在训练期间拿不到收入,由于推迟挣钱的时期而损失的利息,以及接受训练所需的特殊费用,如学费和用在书本和设备上的费用。对于有形资本而言,主要的费用是建造生产资料的支出和在建筑时期所应支付的利息。在这两种情况下,假定个人认为,他的额外报酬超过了额外的费用,可以设想:那个人便会把投资当作为应该进行的事情。在这两种情况下,假使某一个人从事投资,又假使国家既不对投资给与补助,也不对报酬征收赋税,该个人(或他的家长、支助者或捐助人)一般负担所有的额外费用和获得所有的额外报酬:显然不存在系统地使私人动机和社会所认为应有的动机之间具有差异的无人负担的费用和无人获得的报酬。假使投资于人和投资于有形资产的资本是同样容易地得到,不管通过市场或通过有关个人或他们的家长,或他们的捐助人的直接投资,那么,资本的利润率在两个情况中大体上讲会趋于均等。假使它在非人的资本上较高,家长会有为了他们的孩子而购买这种资本的动机,同时,不会相反地对职业训练投入相等的一笔款项。然而,事实上,有相当多的例证表明,对职业训练投资的利润率要比对有形资本投资的利润率高得多。二者的差异说明了存在着对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问题。
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很可能反映了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得到人力投资的资金比得到有形资本投资的资金具有不同的条件而且比较困难。要想知道为什么如此是很容易的。假使一笔固定数量的贷款被用来进行有形资本的投资,贷款者能够以抵押的形式,或对有形资产的一部分有权变卖的形式来减少风险,从而,在不能归还贷款时,可以通过变卖有形资产,至少收回贷款的一部分。假使他贷出一笔相等的款项来增加人的挣钱能力,他显然不能获得任何类似的收回贷款的保证。在一个非奴隶制的国家中,体现投资款项的个人不能被买进和卖掉。即使他能被买进和安排,收回贷款的保证也是相差很远的。有形资本的生产力一般不取决于借款购买它的人的合作。人力资本的生产力却明显地需要这种合作。因此,对某一个人提供职业训练的资金,而此人除了动用将来的收入以外又无法对归还资金提供保证,这一行动要比贷出款项来修建一幢房屋这一行动具有很小的吸引力;归还款项的保证较少,同时,以后收回利息和本银的代价则是非常之大。
对职业训练提供一笔固定数量的资金的不合适之处还包括下列的复杂情况。这一种投资势必牵涉到很大的风险。所期望的收益的平均数可能很高,但是,围绕着平均数的波动却很大。死亡或残废是造成波动的一个显著的原因,但是,它对波动的影响可能比人在能力、精力和运气方面的差异要远为微小。因此,假使借出了固定数量的货币贷款,而归还的保证仅仅是所期望的未来的收入,那末,相当大的一部分永远不会归还的。为了使这种贷款的贷款者感到兴趣,对所有贷款所索取的名义利息率应该是高到足够的程度来补偿由于烂帐而损失的本银。这种高额的名义利息率一方面和禁止高利贷的法律相冲突,同时又使贷款对借款者不感兴趣。为了其他风险很大的投资所采取的应付的方法是入股投资再加上有限的债务责任。在教育上的相应的方法是:“购买”他将来的收入的一部分;给他垫付训练所需要提的资金,其条件为:把他未来收入的指定部分偿付给贷款者。以这种方式,贷款者将从相对成功的个人那里取回比他原来投资要多的金额。这笔金额将补偿他不能从没有成功的个人那里扣回的他原来的投资。
对这种私人契约看来并没有法律上的阻碍,即使它们在经济上相当于购买了一张个人的挣钱能力的股票,因而相当于部分的奴隶制。尽管这种契约对借款和贷款者是可能有利的,为什么这些契约不很普遍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在个人有迁移自由条件下的管理契约的高昂的费用、取得正确的收入报告书的需要以及契约将继续有效的时期的漫长。对于规模微小而借款人在地理上分布很广的投资,这些费用很可能是特别高的。这些费用有可能是这种类型的投资从来没有在私人管理下发展出来的主要原因。
然而,下列各点似乎很有可能也起着主要作用:这种新奇思想的逐渐累积的影响,不愿把对人的投资严格地看作为对有形资产的投资;即使契约是自愿订立的,社会对这种契约会作出不合理的谴责的可能性,以及法律和传统对最适合于从事这种投资的金融机关,如人寿保险公司的限制。尤其对早期新参加者,可能有的营利是如此之大,以致值得为之而负担非常沉重的管理费用。
不管原因为何,市场的不完全性导致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因而,政府的干预可能具有两个为之辩解的合理化的理由,而这两个理由均建立在“技术垄断”之上。就这种投资发展的障碍在于其有行政费用而言,存在着“技术垄断”的情况;以及就障碍来自市场阻力和刚性从而需要对市场运转加以改善而言,也存在着“技术垄断”的情况。
假使政府确实进行干预的话,它应该如何进行呢?一个明显的干预形式,也是迄今一直采取的唯一形式,是由政府用其一般收入的款项来直接补助职业或专科学校教育。这种形式似乎显然是不合适的。投资应该进行到这样的程度,在这个程度,额外的报酬将能偿还投资并且使投资的收益等于市场利息率。假使是对人力投资,额外报酬采取的形式是:个人服务的代价高于他在不受职业训练的情况下所能得到的代价。在一个私人市场经济中,个人将把这种报酬当作为他个人的收入。假使对个人的职业训练投资加以补助,那么,个人并不要负担任何补助的费用。结果,假使把补助给予所有愿意得到训练并且能维持训练最低标准的人,那将趋于造成对人力投资的过多,因为,只要它产生超过私人费用的额外收益,即使收益不足以补偿所投入的资本而且更无利息可言,个人仍然有获得训练的动机。为了避免这种过分的投资,政府必须对补助施加限制。即使不谈计算“正确”投资量的困难,这也涉及以某种实质上是任意行事的方式来把有限的投资配给到超过投资所能维持的申请参加训练的人。那些运气好到足以能拿到补助金来进行训练的人们将取得投资的全部报酬,而费用则被一般的纳税人所负担——是一个完全任意决定和几乎肯定是毫无道理的一次收入的再分配。
这里的要求不是再分配收入,而是使资本按照同样的条件能为人力和有形的投资所用。个人应该自己负担投资的费用和获得报酬。当他们愿意负担费用时,他们不应该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而不能进行投资。达到这个结果的一个方法是让政府对人从事股份性质的投资。政府机构应该对任何能满足最低质量标准的个人的训练提供资金或帮助提供资金。只要资金系用在认可的机构作为训练之用的话,政府可以在规定的年限中,每年提供一定的数量。反过来,个人应该同意,在将来的每一年中,对于他从政府那里得到的每1000美元的费用,付给政府他的收入超过一定基数后的一个特殊百分比。这笔支付能很容易地与所得税的支付合併在一起,从而,所引起的附加行政费用是最小量的。基数应该等于没有这一训练情况下的估计的平均收入,支付的收入的百分比应该被规定在使整个方案收支相抵的水平。按照这个方式,接受训练的个人在实际上负担了整个费用。这样,投资的数量的大小能由个人选择加以决定。假使这是政府给职业或专业训练提供资金的唯一方法,又假设所计算出来的收入反映了一切有关的收益和费用,个人的自由选择会趋向于造成投资的最优数量。 第二个条件不幸地不大可能完全得以满足,因为不可能把上面所提及的非金钱的收益计算进去。因而,实际上,上述办法下的投资仍然会是有点儿过于微小并且不会按最优的方式进行分配。
由于几个原因,私有的金融机构和非利润的机构,如基金会和大学,更加适宜于从事这个计划。由于估计收入基数和付给政府的超过基数部分的收入的困难,那末,就存在着使上述计划变成为政治的足球游戏的巨大危险。各种职业目前收入的资料仅能提供一个粗略的近似值作为计算整个计划是否收支相抵的根据。此外,收入基数和超过基数的部分是因人而异的,取决于事先预计的各人挣钱能力的差异,正象人寿保险费用由于不同的预期寿命而有所不同一样。
就行政费用阻碍这个计划由私人机构加以执行而言,提供资金的政府单位是联邦政府而不是更小的单位。任何一个州会象一个保险公司那样花同样的费用来与接受资金的人们保持联系。联邦政府会把这些费用减少到最少的数量,虽然并不完全消除它。例如,一个移往另一个国家的个人可能仍然在法律上和道义上有义务支付他收入中的事先商定的份额,然而,强制执行这个义务可能是困难和花钱的事情。因而,非常有成就的人们可能有迁移的动机。当然,类似的问题会在所得税的情况下出现,而出现的问题还具有较广泛的范围。在联邦政府一级执行这个计划的行政问题虽然在细节上无疑是麻烦的,但看来并不严重。严重的问题是早已提及的政治问题:如何防止这个计划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足球游戏,并在这个过程中,从一个收支相抵的方案变成为一个补助职业教育的手段。
但是假使这种危险是真实的,机会也是真实的。目前资本市场存在的不完全性趋向于把较为昂贵的职业和专业训练限制在其家长或捐助者有能力向其提供所需的资金的人。通过使许多有才华的人得不到必要的资金,上述家长或捐助者把这些能得到资金的个人变成为能避开竞争的“非竞争性”的集体。结果,在财富和地位上永久存在着不平等的状态。类似上面概述的安排的发展将使人们在较广泛的范围上能得到资本,从而,将在很大的程度上使机会均等成为现实,使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减少并且使人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并不通过对竞争的限制,并不通过对积极性的破坏以及并不通过对表面现象的处理,象单纯的收入的再分配所造成的那样,而是通过加强竞争,通过使积极性更加能发挥作用以及通过消除不平等的原因。
第七章资本主义和歧视
特殊的宗教、种族或社会的集体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具有特殊不利的条件,正象俗语所说,他们是受到了歧视。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歧视已经大为减少,这是一件突出的史实。契约安排替代身份安排是解放中世纪奴隶制度的第一步。犹太人在整个中世纪得到生存的可能是因为有市场部门的存在,在其中,尽管有官方的迫害,犹太人能够工作并且维持他们自己。清教徒和公谊会教徒能够移民到新世界,因为他们能在市场里累积足够的资金去这样做;尽管在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受到限制。在南北战争后,南方各州采取许多措施来对黑人施加法律的限制。在任何规模上从未采取的一个措施是对不动产或动产的所有权设立障碍。没有设置这些障碍显然并不反映对黑人免除限制的任何特殊关怀,而却反映了对私有财产的基本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致能超越了对黑人歧视的愿望。维持私人财产和资本主义的一般法则是黑人的机会的一个主要泉源,并且允许他们比不维持这一法则的情况下取得较大的进展。举一个较为普遍的例子,在任何社会中,保存歧视是性质上最垄断的领域,而对特殊肤色和宗教团体的歧视在具有最大竞争自由的那些领域却是最少。
正象第一章所指出的那样,经验的一个难于理解之处是:尽管有这个历史证据,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主张进行基本性变革的声音最响和为数最多的人往往来自受歧视的少数集团。他们趋向于把他们经历的残余限制归因于资本主义,而不承认自由市场是一个主要因素来使这些限制缩小到它们现有的程度。
我们已经看到,自由市场如何把经济效率和不相关的各种事实相分隔。正象第一章所指出的那样,面包购买者不知道面包是由白人还是黑人、是由基督徒还是犹太人种植的小麦所做成。结果,小麦生产者处于最有效地使用资源的地位,而不管社会可能对他雇用的人员的肤色、宗教或其他特征的态度。此外,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自由市场具有把个人的经济效率和其他特征相分开的经济动机。在商业活动中,具有除了生产效率以外的倾向性的人和没有这种倾向性的人相比,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具有这样的倾向性的个人实际上比没有这样倾向性的其他个人提高了自己的成本。因此,在自由市场中,后者会把前者赶走。
同样的现象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我们往往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即:对不同的种族、宗教、肤色或者任何其他事项进行歧视的人不会由于这样做而蒙受损失,他不过是把代价添加在别人身上。这个观点可以和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的产品上征收关税并不伤害自己的谬论相提并论。两者都是同样错误的。例如,反对从黑人那里购货、或与黑人并排工作的人会因之而限制了他的选择范围。一般说来,他必须为他购买的东西支付较高价格,或为他的工作取得较低报酬。或者,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我们中那些把肤色或宗教看作不相干的人结果能买到一些较为便宜的东西。
这些意见也许能说明,在对歧视下一定义或加以解释时,存在着真正的问题。进行歧视的人会为此而支付代价。他好象在“购买”被他看作为“产品”似的东西。除了一个人不赞同其他人的“口味”以外,很难看出歧视还有任何意义。假使个人愿意付出较高代价倾听一个歌手而不是另一个歌手唱歌,我们不把它看作为“歧视”——或者至少不是同样令人厌恶的意义上的“歧视”,虽然我们会把它看作为“歧视”,假使他愿意付出较高价格而让一种肤色的人,而不是另一种肤色的人为他服务的话。两种情况之间的差异是;在一种情况下,我们赞同这种“口味”,而在另一情况下,我们不予赞同。除了我们同情和同意于一种口味和否定另一种以外,导致要一个漂亮的而不是丑恶的仆人的口味和导致要黑人而不是白人或要白人而不是黑人的口味之间在原则上有无任何区别呢?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口味是同样的好。相反地,我深信,一个人皮肤的颜色或他双亲的信仰本身并不构成应以不同方式对待他的理由;应该根据一个人是什么和在干什么进行判断,而不应根据这些外表特征来进行判断。对于其口味这一方面和我不同的那些人的偏见和狭隘的看法,我感到遗憾并且对他们表示轻视。但是,在一个以自由讨论为基础的社会中,以我而论,适合的办法是设法说服他们,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口味是不好的,从而,应该改变他们的观点和他们的行为,而不要使用强制的力量来把我的口味和我的态度强加于人。
公正就业的立法
公正就业实施委员会曾在许多州中被建立起来,其任务在于防止在就业过程中由于种族、肤色或信仰的原因而受到“歧视”。这种立法显然要引起对人与人之间自愿订立契约的个人自由的干预。它使任何这种契约受到州的批准或不批准。这样,它构成了一种在大多数其他情况下我们会反对的那种对自由的干预。况且,正象大多数其他的对自由的干预一样,受到法律限制的个人很可能并不是那些甚至赞成法律的人希望制裁其行动的人。
例如,有这样一种情况:有一些为邻近居民服务的食品铺,邻近居民非常不愿意从黑人店员那里购买东西。假设食品铺之一有一个店员的职位空缺,而适合于这个空缺的第一个申请店员职位的人恰好是个黑人。让我们设想,由于法律的原因,这家商店必须雇用他。这个行动的影响将是减少这家店铺的生意,而把亏损强加在店铺主的身上。假使公众的偏爱相当强烈,它可能甚至会使店铺关闭。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店主会优先雇用白人而不是黑人作为店员;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不表示任何偏爱或他自己的偏见或口昧。他可能只是传递公众的口味。他好象是在生产顾客愿意为之而付款的劳务。然而,他受到了法律的损害,并且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唯一受到法律损害的人,而该项法律禁止他从事于这种活动,也就是说,禁止他迎合公众的口味来雇用一个白人而不是一个黑人的店员。该法律企图消除其偏好的那些顾客所受到的影响的程度,却由于商店数目的限制,从而他们必须由于一个商店的停业而支付较高的价格。这种分析能够扩大到一般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当雇主们采用把非生产技术性因素当作与就业有关的因素来考虑的政策时,雇主们或是在传递他们的顾客的偏好,或是在传递他们的其他雇员们的偏好。正如上面指出的那样,雇主们具有一种典型的动机:他们会想方设法避开他们的顾客或他们的雇员的偏好,假使这些偏好使他们花费更高的代价的话。
公正就业实施委员会的人争辩道:在就业问题上对人与人之间订立契约的自由进行干预是应该的,因为,当两个人在物质生产能力方面具有均等条件时,拒绝雇用黑人而不拒绝白人的个人就是伤害别人,即: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特殊肤色或信仰的集团的就业机会受到限制。这个论点涉及到严重混淆两种情况非常不同的伤害。一种是积极的伤害,即:一人用体力伤害另一人,或迫使他签订他没有同意的契约。明显的例子是一个男的用铁头棍棒打另一个人的头。不太明显的例子是在第二章里论述过的溪水污染。第二种是消极的伤害,它发生于两个人不能找到相互可以接受的契约的时候,就象在我不愿意购买某人要向我出售的一些东西时一样。因此,我使他处于比我买这些东西时较为不利的地位。假使整个社会偏好爵士乐的歌手,而不是歌剧的歌手,它肯定会增加相对于后者而言的前者的经济福利。假使一个爵士歌手能找到工作,而一个歌剧歌手却不能,这仅仅意味着:公众认为值得为爵士歌手的劳务而花钱,而歌剧歌手却不值得。这位歌剧歌手是受到公众的口味的“伤害”。假使人们的口味相反,他将处于较优的地位,而爵士歌手则受到“伤害”。显然,这种伤害非不涉及任何不自愿的交换,或使第三方负担费用和得到好处。我们具有充分的理由能使用政府以防止一人向另一人施加积极的伤害,也就是说,防止使用强迫手段。但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能使用政府以避免消极的“伤害”。相反地,这种政府干预会减少自由和对自愿的合作施加限制。
把公正就业实施委员会的立法所接受的原则应用于其他的问题会使该法的支持者几乎全会感到憎恨。假使政府能说,个人不应由于肤色或种族或宗教而在就业上受到歧视,那末,政府也同样能说,个人应该由于肤色、种族和宗教而在就业上受到歧视,如果多数人投票赞成的话。希特勒的纽伦堡的法律和限制黑人权利的南方各州的法律都是和公正就业实施委员会在原则上相类似的法律事例。反对这些法律而又赞成公正就业实施委员会的人不能进行争辩:说它们在原则上有任何不妥之处。说这些法律牵涉到不应容许的国家的行动。他们只能说:这一特殊的判别标准是与事无关的。他们只能设法说服其他人,应该使用其他的,而不是上述的判别标准。
假使我们浏览历史并且考察根据事例本身的优缺点而不根据某种一般原则加以判别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说服而取得多数赞成的事例,那末,不容置疑,广泛地接受政府在这一领域采取行动的合理作用是极端不利的;即使从目前赞成公正就业的人的观点来看,也是如此。如果说目前的支持公正就业的人是处在一个使他们的观点付诸实施的地位,这仅因为宪法和联邦政体的原因;它们使得在国家一部分的地区的多数派可以把它的观点强加于国家另一地区的多数派。
作为一般的原则,任何指望特殊多数派的行动来保卫它的利益的少数派是目光极端短浅的。接受适用于一类事例的一般性的自我克制的规定可以禁止特殊的多数派刻意压制特殊的少数派。在没有这种自我克制规定的情况下,多数派肯定会使用他们的权力使他们的偏好生效,或者可以说,使偏见有效,从而不保护少数人免于大多数人的偏见。
以另外一种方式,或许更为明显的方式来说,考虑一下某一个人。此人相信目前那种口味的型式是不好的,并且相信黑人具有比他认为所应有的就业机会较少。设想只要存在着许多在种族以外其他条件大致相等的职业申请者时,他会遵照他的信念,总是选择黑人申请者。在目前情况下,是否会阻止他这样做呢?显然,公正就业实施委员会的逻辑是他应该受到阻止。
除了就业以外,这些原则最经常发生作用的领域或许是言论的领域:相当于“公正就业”应该是“公正言论”,而不是自由言论。在这一方面,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观点看来似乎是极端自相矛盾的。它赞成言论自由同时又赞成公正就业法。表明主张言论自由的理由的一个方式是:我们不相信短暂时期中的多数派能够在任何时候决定什么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言论。我们需要一个言论的自由市场,从而,即使某一言论在最初仅为几个人所赞同,它也能获得机会来赢得大多数人或几乎一致的赞同。恰好是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就业或更一般地适用于物品和劳务市场。由短暂时期中的大多数来决定什么是就业的条件比决定什么是正确的言论是否更为可取呢?的确,假使物品和劳务的自由市场遭到破坏,言论的自由市场能长期维持下去吗?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将为保护种族主义者在街头宣传种族隔离主义的权利而战斗到底。但是,假使他为了实现他的原则而拒绝雇用黑人来从事其一具体工作,该协会却赞成把他投入监狱。
正象早已着重指出的那样,对于我们这些相信类似肤色这样的特殊条件与就业无关的人而言,适当的办法是说服我们的同胞成为具有同样见解的人,而不使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来迫使他们按照我们的原则行事。在所有的团体中,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应该是第一个认识到和承认这一事实的人。
劳动权利法
有些州已经通过所谓“劳动权利”法。这些法律禁止把加入工会作为取得就业职位的一个条件。
劳动权利法与公正就业实施委员会所牵涉到的原则是相同的。两者均干预就业契约的自由;一种情况规定,特殊的肤色或信仰不能被当作为就业条件;另一种情况则为,工会会员的资格不能被当作为就业条件。尽管原则相同,关于这两个法律,在观点上几乎有100%的分歧。几乎所有赞成公正就业的人反对劳动权利法;几乎所有赞成劳动权利法的人反对公正就业。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对两者都反对,正如我同样反对禁止所谓“黄狗”契约(以不加入工会为条件的就业契约)的法律一样。
在雇主们和雇员们之间存在着竞争的条件下,似乎没有理由认为:为什么雇主们不应该有自由来对他们的雇员们提出他们需要的条件。在有些情况下,雇主们发现雇员们宁肯接受福利方面的东西作为报酬的一部分,如棒球场地或消遣设备或较好的休息设备,而不是现金。同时,雇主们发现提供这些设备作为他们的就业契约的一个部分而不是提供较高的现金工资是更为有利可图的。雇主也同样地可以提供养老金计划,或要求参与养老金计划,等等。这里没有任何一点涉及任何对个人寻找工作自由的干预。这只是反映着雇主企图想使工作的条件适合于雇员并且对他有吸引力。只要存在着很多雇主,具有各种特殊需要的雇员将有可能在相应的雇主那里找到工作来满足他们。在竞争条件下,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限雇原则。假使事实上有些雇员宁愿在有限雇原则的厂商工作,而其他人宁愿在有泛雇原则的厂商工作,那就会发展出不同形式的就业契约;有些人得到一种条文规定,而其他人得到其他的条文规定。
当然,作为实际的事物,在公正就业实施委员会和劳动权利之间具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差异是:在雇员的一边,出现以工会组织形式的垄断和关于工会的联邦立法的存在。在一个竞争的劳务市场中,雇主们提出限雇原则作为就业条件是否有利可图是令人怀疑的。在劳工一边的工会往往没有强大的垄断力量的情况下,限雇原则从来不会存在。它几乎总是垄断力量的一个象征。
限雇原则和劳工垄断的一致性并不能构成支持劳动权利法的一个论点。不论垄断的形式和表现的方法如何,它是一个应为消除垄断力量而采取行动的论点。这是一种要求在劳动市场采取更为有效和普遍的反托拉斯的行动的论点。
另一种在实践上为重要的特点是:联邦法和州的法律之间的冲突以及在目前适用于所有的州的联邦法在州中留下了漏洞,需要通过劳动权利的法律加以弥补。最优的解决办法将是重新修订联邦法。困难是没有任何一个州能实现这一点,然而,在一个州里的人们可能希望在他们州内管理工会组织的立法有一个变化。劳动权利的法律可能是唯一有效的办法,从而具有最小的坏处。部分地由于我倾向于相信:劳动权利法律仅就它本身而论,不会对工会垄断力量有任何巨大的影响,我不接受上述为劳动权利法的存在而提出的理由。以我看来,认为劳动权利法律在实践上有意义的辩护论点似乎远为太弱,以致不能压倒对该法的原则的反对意见。
学校教育的种族隔离
学校教育的种族隔离引起了以前的论述没有提到的一个特殊问题,其所以如此,仅具有一个原因。原因是:在目前情况下,学校教育主要是由政府所经营和管理。这意味着,政府必须作出明确的决定。它必须强制执行种族隔离或者种族同校,二者必居其一。以我看来,二者均不是好的解决办法。我们这些人相信肤色是无关的特征,并且认为,所有的人应该承认这一点。然而,我们又相信个人自由。因此,我们面临着两难的局面。假使一个人必须在强制性的种族隔离和强制性的种族同校的坏事之间进行选择,我自己则不可能不选择种族同校。
在写作前面一章时,我并不考虑隔离和同校的问题。它却恰当地提供了能避免两种坏事的解决办法——这很好地说明了旨在于增加一般自由的安排如何能解决具体的自由的问题。恰当的解决办法是消除政府对学校的经营,并且准许家长把他们的孩子送进他们要孩子进的那种学校。此外,我们当然要尽可能地用行为和言论来培植会导致种族混合学校成为常规的态度和意见,而种族隔离学校则成为少数的例外。
假使建议象前一章那个建议一样被采用的话,它将准许不同类型的学校得以发展,有些全是白人,有些全是黑人,有些是混合的。随着整个社会态度的改变,它将准许一类学校逐步过渡到另一类学校——希望过渡成混合的学校。它会避免一直在加大的社会紧张程度和瓦解社会的严酷的政治冲突。对于这个特殊领域,正象市场对于一般领域那样,它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而又不要求服从。
弗吉尼亚州采取了与前章所概述的具有许多共同点的计划。虽然采取该计划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强制性的种族同校,我可以预言,上述计划的最后的效果会是很不相同的——无论如何,动机和效果之间的差异是赞同自由社会的主要理由之一。应该让人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图行事,因为,没有办法去预测其后果如何。的确,甚至在执行的早期,后果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有人告诉我:在第一批要求给予票证来更换学校的各种人中,一种是想把孩子从隔离的学校转移到种族同校的学校。要求转学不是出于有关种族的目的,而只是因为种族同校的学校在教育上办得较好。进一步往前看,假使票证制度不被废除的话,弗吉尼亚州会提供一次实验来检验前一章结论。假使那些结论是正确的,我们应该看到弗吉尼亚州的学校的兴旺状况,其中存在着学校多样化的增加、重点学校质量的相当程度(如果不是很大的话)的提高以及由于重点学校的影响而随后出现的其他学校的质量的提高。
在事物的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那么天真,以致认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信念能由法律在短暂时间内来根除掉。我住在芝加哥。芝加哥没有强迫隔离的法律。它的法律要求种族同校。然而事实上,芝加哥的公立学校很可能和大多数南部城市的学校一样完全存在着种族隔离。假使弗吉尼亚制度能在芝加哥使用,结果几乎无疑地是:隔离会相当大地减少,而对最能干和最有志气的黑人青年,社会提供的机会则会大为扩大。
第八章垄断以及企业和劳工的社会责任
竞争有两个非常不同的意思。在一般的论述中,竞争的意思是个人之间的争胜;在其中,人人设法胜过他的已知对手。在经济事务中,竞争几乎意味着相反的事物。在竞争市场上,没有个人的争胜,没有个人的讨价还价。在自由市场内,种植小麦的农民并不觉得自己在和事实上为自己的竞争者的邻居进行个人竞争或受到他的威胁。竞争市场的本质是它的非个人的特征。没有一个参与者能决定其他参与者将会有获得物品或工作的条件。所有人都把价格高作为市场决定的事实,而对于价格,每个人只能具有微不足道的影响,虽然所有参与者在一起决定由他们各自的行动的共同影响而决定的价格。
当一个特殊的个人或企业对一个特殊的物品或劳务具有足够的控制力在很大的程度上来决定其他个人获得物品或劳务的条件时,垄断就存在。在某些方面,垄断比较接近于一般的竞争概念,因为它的确涉及个人的争胜。
对于自由社会,垄断引起两类问题。第一,通过减少个人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垄断的存在意味着对自愿的交换进行限制。第二,垄断的存在引起逐渐被称为垄断者的“社会责任”的问题。竞争市场的参与者没有多少力量来改变交换条件;作为一个单独存在的实体,竞争者是难于辨认的。因此,除了所有公民都必须遵守的本地的法律和根据他的观点而生活以外,很难说他具有任何“社会责任”。垄断者是可以辨认的并且具有权力。我们不难争辩:垄断者应该使用他的权力,不仅仅助长他自己的利益,而且要促进社会上可取的目标。然而,广泛地使用这种说法会毁灭一个自由社会。
当然,竞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象欧几里得几何中的线或点那样。没有人看到过欧几里得的线——它的宽度和厚度均为零——然而,我们大家认为把许多欧几里得的容量——例如勘测者的绳索——看作为欧几里得的线是有用的。同样的,不存在象“纯粹”竞争这样的东西。不管他的影响如何地微小,每个生产者都对他生产的物品价格具有一些影响。在理解和在政策上的重要问题是,这个影响是否很重要或是否能被忽视,正如勘测者能忽视被他称为“线”的这个东西的厚度一样。回答当然必须取决于具体的情况。但是,当我研究了美国的经济活动以后,我逐渐感到:应该把经济制度看作为竞争性情况下的问题和企业具有非常广阔的范围。
垄断引起的问题是技术性的并且涉及到我在其中没有特殊研究的领域。由于这个原因,本章局限于对某些一般性的问题作出相当概略的论述:垄断的范围、垄断的来源、政府应采取的政策以及企业和劳工的社会责任。
垄断的范围
有三个重要的垄断问题的领域需要分别加以考虑:企业垄断、劳工垄断和政府所造成的垄断。
1.企业垄断。关于企业垄断,从整个经济观点来看最重要的事实是它的相对的不重要性。在美国,大约有四百万个单独经营的企业。每年成立的新企业大约为四十万个。每年关闭的企业的数目大约稍小一些。自我雇用的人接近于占劳动人口的五分之一。在人们所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企业中,巨人和侏儒并肩而存。
除了这些一般印象外,很难提出令人满意的客观的方法来衡量垄断和竞争的范围。主要的原因已经在上面提到:这些在经济理论上使用的概念是理想的事物,其目的在于分析特殊的问题,而不是描述目前的情况。由于这个原因,对一个具体的企业或行业能否被看作为是垄断的或竞争的并没有明确的决定办法。由于很难对这些名词的意义作出解释,这一事实已经导致了大量的误解。同一个词可用来指不同的东西,取决于判断竞争状态的经验背景。最显著的例子也许是美国学者称之为垄断的范畴。同一范畴会被欧洲人看作为很有竞争性的概念。结果,欧洲人按照竞争和垄断在欧洲的意义来解释和讨论美国的文献,从而,趋于相信美国的垄断程度比事实上存在的大得多。
大量的,尤其是G.沃伦·纳特和乔治·J.施蒂格勒的研究成果,试图把企业分类成为垄断的、有效竞争的和政府经营或监督的,并且找出这些范畴里的企业在不同时间中的变化。他们作出结论:在1939年,整个经济的大约四分之一可以被当作为政府经营或监督的。在剩余的四分之三中,至多四分之一或许少到15%能被当作为垄断的,而至少四分之三或许多至85%能被当作为竞争的。政府经营或监督的部分当然在过去半个世纪左右大为增长。另一方面,在私有部门内,看来不存在任何垄断范围增加的趋势,而它很可能还有所减少。
我怀疑,存在着广泛的印象认为垄断不但比这些估计数字所表明要远为重要,而且还随着时间的进展而持续增大。造成这个错误印象的原因之一是把绝对的大小和相对的大小混淆起来。随着整个经济的增长,企业的绝对大小变为更大。这就被认为是指它们占有市场的较大部分,而事实上市场可能比企业增长得甚至于更快。第二个原因是垄断更具有新闻价值,从而使得人们对它比对竞争更加注意。假使请一般人列出美国主要行业的名单,那末,几乎所有人会在该名单中写进汽车生产,而很少人会写进批发生意。然而,批发生意却比汽车生产重要两倍。批发生意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因而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很少人能举出在批发生意中的主要企业的名称,尽管其中有几个在绝对规模上是很大的。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高度竞争性,然而,从事汽车生产的厂商的数目却远为较少,从而肯定比较接近于垄断。每个人能说出生产汽车的主要公司的名称。引用另外一个显著的例子:家庭服务业比电报和电话业更为重要得多。第三个原因是过分强调在大与小对立中的大的重要性的一般偏见和趋向。关于这一偏见和趋向前面一点仅是一个特殊的表现。最后,我们社会的主要特征被认为是它在工业上的特征,这导致对经济中的制造部门的过分强调,而这一部门仅占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产量或就业量。同时,垄断在制造业中比在经济的其他部门中更为流行得多。
由于许多同样的原因,伴随着对垄断重要性的过分估价而来的是对那些在垄断与竞争之间更加偏于促进垄断的技术变化重要性的过分估价。例如,非常强调大规模生产的扩展。运输业和电讯业的发展却得到了很少的注意;而通过减少地区市场的重要性和通过扩大竞争的范围,这两个行业可以促进竞争。汽车业的不断增长的集中程度为众所知,而能减少对大铁路公司依赖的卡车运输业的增长却无人注意。对钢铁行业的集中程度的减退也是如此。
2.劳工垄断。在劳工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对垄断的重要性的过分估价。工会包括大约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而这一事实大大地过分估计了工会影响工资结构的重要性。许多工会是完全不起作用的。甚至于强大有力的工会对工资结构只能发生有限的影响。劳工的事例要比企业的事例甚至可以更加清楚地表明为什么存在着过分估价垄断的重要性的强烈趋势。在有工会的条件下,任何工资增加都要通过工会,即使工资增加并非工会组织的影响。近年来,家庭仆役的工资增长很大。假使存在着一个家庭仆役工会,工资的增加也将通过工会,并且会把此事归因于工会。
这并不是说工会是不重要的。正象企业垄断那样,它们在使许多工资率不同于由市场单独决定的工资率方面起了一个重要和有意义的作用。过低估价和过高估价它们的重要性都是相同程度的错误。我曾作了一个粗略的估计,即:由于工会的存在,大致在10-15%之间的工作人口得到大约10-15%之间的工资率的提高。这意味着大约85—90%之间的劳动人口的工资率减少了大约4%。自从我作了这些估计以来,其他人作了更为详细得多的研究。我的印象是:他们得到的结果大致和我得到的差不多。
假使工会在一特殊的工种或行业中提高工资率,它们势必使那个工种或行业中所使用的就业人数要少于原来的数量——正象任何更高的价格会削减购买量一样。结果是:寻找其他工作的人数增加,其他工种的工资被迫下降。由于工会一般地在总是得到高工资的工人集体中间力量最为强大,它们的影响使得高工资的工人以牺牲低工资工人的利益作为代价来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通过扭屈劳动的正常的使用方式,工会不仅损害整个社会和工人的利益;同时,通过减少条件最差工人可能有的机会,它们也使工人阶级的收入更不均等。
以一个方面而论,在劳工垄断和企业垄断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差异。过去半个世纪里,虽然企业垄断的重要性似乎没有任何上升的趋向,而劳工垄断的重要性却肯定增加。工会的重要性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有着显著的增长,在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初期下降,而在新政时期有过巨大的跃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工会巩固了它们的增进的地位。较近期间它们刚好保持原有的规模或甚至有所下降。下降并不反映在特殊工业或工种内的一种下降,而代表:相对于工会力量弱小的某些行业或工种而言,工会特别强大的行业或工种的重要性的下降。
在劳工垄断和企业垄断之间,我根据一个方面而划出同差别是非常突出的。在某种程度上,工会的作用是加强出售产品时的垄断的一个手段。最明显的例子是煤炭。格非煤炭法企图对煤矿经营者的规定价格的卡特尔提供法律的支持。在三十年代中期,当该法被宣布为违反宪法时,约翰·L.刘易斯和矿工联合工会却填补了留下来的漏洞。不管什么时候,当开采出来的煤产数量多到有可能迫使煤炭价格下降时,刘易斯通过罢工或怠工来控制产量,从而在煤矿经营者的默契的合作之下控制价格。从这种卡特尔的经营办法所获得的好处则在煤矿经营者和煤矿工人之间瓜分。矿工的好处表现为较高工资率,而这当然意味着较少的矿工的就业量。因而,只有那些能保留职位的矿工分享了卡特尔带来的好处,甚至于他们也只能以较多闲散时间的形式来取得很大部分的好处。工会之所以可能发生如此的作用,原因在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不把工会当作为垄断组织。很多其他工会曾经利用了这一点。它们应该更恰当地被看作为是为出售使工业卡特尔化的劳务的企业,而不是工会组织。卡车司机工会也许是最明显的一个。
3.政府和政府支持的垄断。在美国,直接生产商品出售的政府垄断不太广泛。邮局、电力生产、如田纳西河域管理局和其他政府所拥有的发电站;间接通过汽油税或直接通过使用税来提供的公路设施以及城市供水和类似的工厂是主要的例子。此外,有由于存在着象目前这样巨大的国防、空间和研究的预算,联邦政府实质上成为很多企业和整个行业的产品的唯一购买者。这便引起了保持一个自由社会的非常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和最适宜于放入“垄断”的标题下的问题并不属于同一类型。
在私有生产者之间利用政府来建立、支持和实施卡特尔和垄断的安排比政府的直接的垄断增长远为迅速并且在目前也远为重要。州际商业委员会是一个早期的例子,而它的范围已经从铁路扩展到了卡车运输和其他交通工具。农业方案无疑是最突出的。它基本上是一种政府强迫实施的卡特尔。其他的例子是联邦电讯委员会,对无线电和电视进行控制;联邦动力委员会,对进入州际贸易的石油及煤气进行控制;民用航空委员会,对民航公司进行控制;以及由联邦储备局对银行的定期存款的最大利息率的规定,以及在法律上禁止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
这些例子属于联邦的一级。此外,在州和地方各级,类似的发展曾大量增长。就我所知,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与铁路无关,它通过限制油井出油的天数来对油井产量进行限制。它这样做的名义上的理由是保护资源,但在事实上的目的则是为了控制价格。最近,它由于联邦对石油进口施加限额而得到强烈支持。我认为,另一种形式的“羽毛填被”,即:使油井在大多数时间中闲着以便维持价格似乎完全相当于对柴油机车的闲着的司煤炉工人支付报酬。然而,某些用最大声音谴责劳工方面的羽毛填被,认为它侵犯自由企业的一些企业的代表们——显著地在石油工业本身——对石油方面的羽毛填被不闻不问。
在下一章将讨论的营业执照的规定是州一级政府所创造和支持的垄断的另一个例子。对出租汽车的辆数的限制可以说明在地方一级类似的限制。在纽约,表示有权独立经营出租汽车的标记现在售价约为20000美元到25000美元;在费城售价为15000美元。在地方一级的另一个例子是制订建筑的条文规定,外表上是为了公众的安全,但事实上一般被控制在当地建筑工会或私人营造厂协会之下。类似的限制为数众多,而且被施加于城市和州一级许多不同的活动。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对个人之间自愿交换的个人能力施加任意的限制。它们同时限制自由和促使资源的浪费。
有一种政府所创造的垄断在原则上和迄今所考虑的那些垄断很不相同,即:给发明者以专利权和给作家以版权。这些是不相同的,因为,它们能同样地被看作为属于财产权的范畴。按照实际的意义来说,假使我对一块特殊的土地具有财产权,我也可以被说成为对于那块土地具有政府所规定和强制执行的垄断权。就发明和出版而言,问题为是否有必要建立一种类似的财产权的范畴。这问题是利用政府规定什么可以被看作为财产,和什么不被看作为财产一般需要的一部分。
以专利权和版权而论,显然存在着足够的理由来把它们规定为属于财产权的范畴。除非是这样做,发明者会发现,为了他的发明在生产上所作的贡献而收集费用是困难的或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他给与别人他不能取得报酬的利益。因此,他会没有积极性来投入发明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作家。
同时,还涉及费用问题。首先,有“许多发明创造”是不可能给予专利权的。例如,超级市场的“发明者”把巨大的利益给与他不能向之收费的同胞们。就各种发明需要同样的能力而言,专利权的存在趋于使活动转向于可以取得专利的发明。再者,可有可无的专利权或其合法性可能在法庭上引起怀疑的专利权常常被用作为维持私人相互勾结的安排的一种办法;否则,相互勾结的安排就很难维持或根本不可能被维持住。
这些是对困难和重要的问题非常表面化的说明。它们的目的并不想提出任何具体的答案,而仅想说明为什么专利权和版权的类型不同于政府支持的其他垄断的类型,以及说明它们所引起的社会政策问题。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附着于专利权和版权的特殊条件——例如,给与专利保护十七年,而不是其他时期——这不是原则问题。它们是由实际考虑来决定的适合与否的问题。我本人倾向于相信:专利保护的期限应该远为较短。但这是对一个问题的随意的判断,而对这问题曾经有过许多详细的研究,并且需要很多进一步的研究。因而,我的意见不值得重视。
垄断的来源
垄断有三种主要来源:“技术”方面的原因、政府的直接和间接支援和私人之间的相互勾结。
1.技术方面的原因。正如在第二章里所指出的那样,垄断在某种程度上起源于技术方面的原因,因为,技术考虑使得一个企业而不是有许多企业的存在成为有效率和经济的办法。最明显的例子是电话系统、供水系统以及在单个社会中类似的东西。遗憾的是:并没有解决技术垄断的好办法。只存在着三个坏的可供选择的途径:不加控制的私人垄断、国家控制的私人垄断以及政府经营。
我们似乎不可能说这些坏途径的任何一个在一切情况下都比其他两个要好一些。如在第二章里所说的那样,政府调节或政府经营的垄断的巨大缺点是政府非常难以退回不管。由于这个原因,我倾向于相信: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坏处最少的是不加调节的私人垄断。动态的变化很可能减少它的垄断的作用,然而,在这里,至少存在着允许动态变化发生作用的某些机会。甚至在短期内,一般存在的代用品似乎比初看起来要多,所以私人企业能使价格高于成本以便牟利的程度具有相当狭窄的范围。此外,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进行调节的政府机关它们自己常常倾向于受到被调节的厂商的控制之下,从而,在政府调节下的价格未必比没有调节下的价格要低。
很幸运的是,技术考虑使垄断成为可能或现实的领域是相当有限的。假使不把以技术垄断为理由而造成的政府调节的趋向扩大到不适用的情况,技术垄断不会对保存自由经济施加严重的威胁。
2.政府直接和间接的支援。垄断力量的最重要来源也许是政府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援。许多相当直接的政府支援的例子已经在上面加以引用。对垄断的间接支援包括为了别的目的所采取的措施。它们主要是这些措施的副作用,对目前公司的潜在的竞争者加以限制。其中三个最明显的例子也许是关税、赋税以及有关劳工纠纷的强制性的法律和立法。
关税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保护”国内的企业,它们意味着对潜在的竞争者设置阻碍。它们总是干预个人参与自愿交换的自由。自由主义者毕竟把个人,而不是国家或特殊国家的公民作为他的等同的单位。因此,假使不让美国和瑞士的公民进行双方互利的交换,自由主义者把它看作为对自由的侵犯,正象不让美国的两个公民这样做一样。关税不一定造成垄断,假使受到保护的行业的市场大到足够的程度,而技术条件又允许很多公司的存在,那末,正象在美国的纺织业里一样,受到保护的行业在国内能存在着有效的竞争。然而,关税显然还是助长垄断的。由少数几家厂商比由许多厂商串通起来制订价格要容易得多,而一般说来,由同一国家的企业比不同的国家企业串通起来制订价格较为容易。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而防止了广泛扩展的垄断,尽管英国的国内市场范围相对微小,而且具有许多大规模的厂商。自从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然后以较广泛的范围在三十年代早期放弃了自由贸易以来:垄断在英国已经成为远为严重的问题。
赋税立法的影响甚至于更为间接,而却不是更不重要。一个主要的因素是个人和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中关于资本增益的特殊处理的结合。我们假设:一家公司纳税后的收入为1000000美元。假使它把整个1000000美元付给它的股东作为股息,他们必须把这笔款项算作为他们应据以纳税的收入的一部分。假设他们平均起来应该缴纳这个额外收入的50%作为所得税。这样,他们只能有500000美元可以使用于消费或储存和投资。假使这家公司不付给股东现金股息,它就有整个100万美元作为内部投资。这种再投资会趋向于提高它的股票的价值。在分配股息情况下本来就想把股息储存起来的股东可以简单地把股票保持下去,从而推迟税款的支付一直到他们出售股票时为止。他们和在较早时期为了消费而出售股票的其他人一样,将按低于普通收入税率的资本增益的税率付税。
这种征税的结构鼓励公司把利润保留在公司之内。即使在公司之内的款项所能赚取的利润率远低于股东自己把该款项投资于公司之外所能赚取的利润率,由于税款的节约,在公司内部投资仍然是可取的。这会导致资金的浪费,导致它被使用于生产力较小的目的,而不是较多的目的。由于厂商为它们的利润寻找出路,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横向多样化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也是已经具有基础的公司超过新成立的企业的力量的一个巨大泉源。已经具有基础的公司可以比新成立的企业具有较小的生产力,然而,它们的股东们还是具有对它们进行投资的积极性,而不是把收入取出来,以便通过资本市场把它投入于新的企业。
劳工垄断的一个主要来源是政府的支援。上面论述过的营业执照、建筑物规定,以及类似的其他项目是其中一个来源。给与工会特殊权利的立法,例如不受反托拉斯法制裁、对工会责任的限制、出席特殊法庭的权利以及其他等等,是第二个来源。重要性和上述两点的任何一个相等或较大的是一般舆论的风尚和法律的执行。它们对有关劳工纠纷的事件采取不同于其他事件的标准。假使由于完全的恶意或在进行私人报复的过程中有人把车子开翻或毁坏了财产,没有人会伸出手来保护他们免于法律上的后果。仅使他们在劳工纠纷的过程中有同样的行动,他们或许可以完全免于处分。引起实际或潜在的暴力或高压的工会行动不太可能发生,假使它不是由于当局的默许的话。
3.私人的勾结。垄断的最后的一个来源是私人的相互勾结。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即使为了娱乐和消遣,经营同一行业的人们很少能相聚在一起而又不以相互勾结、反对社会利益的谈话或以某种提价的策划来结束会见”。因而,这种相互勾结或私人卡特尔的安排不断在发生。然而,除非它们能取得政府对它们的支援,它们一般是不稳定的,而时间是短暂的。由于能提高价格,建立卡特尔会使局外人进入该行业更加有利可图。此外,由于较高价格的建立只能由参与者把他们的产量限制在低于他们想按固定价格进行生产的水平,所以,每个人都有积极性来削减价格,以便扩大生产。当然,每个人希望其他人遵守他们之间的协议。只需要一个或几个“骗子”——他们确实是有益于公众的人——来拆散这个卡特尔。在没有政府支援的情况下,卡特尔几乎肯定会非常快地被拆开。
反托拉斯法的主要作用是制止这种私人勾结。在这一方面,它们通过诉讼而取得的主要成就要小于通过间接的影响而取得的成就。它们排除了明显的相互勾结的办法——例如为了达到这个特殊的目的而大家公开地联合在一起——从而,相互勾结的代价更为昂贵。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重新肯定了习惯法的原则,即:为了限制贸易而进行的联合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在各个欧洲国家里,对于一群企业所缔结的通过同一机构出售并向违反者处罚的协定,法院承认协定在法律上生效。在美国,这种协定在法律上无效。这个差异是为什么卡特尔一直在欧洲国家比在美国更为稳定和普遍的主要原因之一。
政府应有的政策
在政府政策的范围内,第一个和最迫切需要的,是消除那些直接支持不论是企业还是劳工垄断的措施,并且对企业和工会以同样的态度执行法律。两者均应从属于反托拉斯法,两者在关于破坏财产和干涉私人活动方面应该在法律上同样对待。
除此以外,减少垄断力量的最重要和有效的步骤便是广泛地改革赋税法。公司税应该取消。不管是否如此做,应该要求公司向股东分摊没有作为股息支付出去的利润。这就是说,当公司发出股息支票时,它要附上一个声明,说明:“除了每股若干股息以外,你的公司还为每股赚了已经用于再投资的若干钱。”这样,就得要求个人股东把他的股息和已经分摊到还没有发给的红利都填入所得税的报税单。公司仍然可以自由地保留任何数量的利润,但是,他们保留利润只能具有正确的动机,即:它们内部投资能赚取的比股东的外部投资能赚取的要多。在使资本市场具有活力、刺激从事企业的精神和促进有效竞争的方面,很少有措施能起着更大的作用。
当然,只要个人所得税象现在那样高度的累进,就会有强大的压力来寻找避免它的冲击的方法。以这种方法和直接的方法,高度累进的所得税构成了对有效使用我们资源的一个严重阻碍。应有的解决办法是大量地减少偏高的税率以及消除已经在法律里体现的逃税方法。
企业和劳工对社会的责任
认为公司和劳工的领导人具有超过自己的股东和会员利益之上的“社会责任”的观点已经得到广泛的接受。这种观点表明了对自由经济的特性和性质的一个基本上的误解。在这种经济中,企业仅具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利用它的资源和从事旨在于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这就是说,从事公开的和自由的竞争,而没有欺骗或虚假之处。同样,劳工领导人的“社会责任”是为他们工会会员的利益服务。我们这些其余人的责任是建立一个法律制度,以便使个人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再度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我从来没有看到那些自称为了社会利益而从事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公司领导人接受除了尽可能为自己的股东牟利以外的社会责任是一种风尚,而很少有风尚能比这一风尚更能如此彻底地损害我们自由社会的基础。这在基本上是一个颠覆性的说法。假使企业家除了为其股东赚取最大的利润以外,确实具有社会的责任,他们又怎么知道责任如何呢?毛遂自荐的私人能否决定社会利益如何吗?他们能否决定为了既定的社会利益加在他们自己或他们的股东身上的负担究竟有多大才是合适的?关于税收、开支和控制这些公共的职责,是否可以容忍完全由私人集团所选择的正好在某些企业中任职的人们去执行吗?如果企业者是公职人员而不是股东们的雇员,那末,在民主政体中,他们迟早会通过选举和任命的公开方式而被推选出来。
在这一事实出现的很久以前,他们决策的权力应该已经从他们那里取走。一个戏剧性的范例,是1962年4月美国钢铁公司取消了钢铁的提价。对于提价,肯尼迪总统表示愤怒,并且以使用报复手段相威胁,包括使用从反托拉斯诉讼到检查钢铁公司领导人的税务报告等各种大小的办法。这是一个触目的事件,因为它显示了集中于华盛顿的巨大权力。这使我们全都注意到我们具备的警察国家所需要的权力已经有多少。它也能很好地说明了目前的要点。假使钢铁价格象社会责任的学说所声称的那样,是一个公众的决定,那末,就不能允许由私人的方面这样做。
这个例子所说明的和最近一直是很突出的学说的一个特殊方面是:所谓企业和劳工的社会责任来压低价格和工资率以便避免价格通货膨胀。假设在某一时期,物价具有上涨压力——当然,最后反映了货币数量的增加——每个企业家和劳工领袖接受了这个责任,又假设他们能使任何价格不致上升,所以我们具有自愿的价格和工资控制而没有公开的通货膨胀。结果会是什么呢?显然是产品短缺、劳工短缺、半黑市和黑市。假使不运用价格来把物品和劳动分配给各种使用的途径,那末,势必要用一些其他手段来这么做。其他的分配手段可能是私人的吗?在某个小而不重要的领域也许暂时会如此。但是,假使涉及到的物品是多而重要的,那末,必定会有压力,或许是不可抗拒的压力,要求政府分配物品,要求政府执行工资政策和要求政府执行调拨和分配劳工的措施。
假使能有效地加以实施,不管是法律上的或自愿的物价控制,最后会导致自由企业制度的毁灭而被中央控制制度所代替。同时,它甚至于在防止通货膨胀方面也不是有效的。历史提供了大量例证,即:决定价格和工资平均水平的是经济制度中的货币数量,而不是企业家或工人的贪婪程度。政府要求企业者和劳工自我克制,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来管理政府自己的事务——包括控制货币在内——也因为人类天然的推缷责任的倾向。
在社会责任领域内,我认为有义务简略论述一个主题,因为它影响我个人的利益。这个主题是:认为企业应该出钱支持慈善事业,尤其是支持大学。在一个自由企业社会中,这种出钱的方式是不合适的使用公司资金的办法。
公司是拥有它的股东的一个工具。假使公司捐赠款项,那会使股东不能自己决定地应该如何处理他的资金。由于公司税和捐赠款项减免征税的规定,股东当然会愿意要公司为他们而捐赠款项,因为,这能使他们捐赠的款项加大。最好的解决办法将是废除公司税。但是,只要公司税存在,就没有理由来允许对慈善和教育机关的捐赠减免税款。这些捐赠应该由我们社会中最终的财产所有者个人来做。
以自由企业的名义企图扩大这种公司捐赠来减免税款的范围的人基本上是违反他们自己利益行事。经常出现的反对现代企业的主要论点之一是有关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问题——即:公司已变成本身具有规律的一个社会机构;在其中,不负责任的公司职员不能为其股东的利益服务。这种指责是错误的。但是,现在的政策的移动方向,即:准许公司对慈善事业捐赠的款项减免所得税的方向,是走向在所有权和控制权之间制造真正分离的方向的一个步骤,也是走向损害我们社会基本性质和特性的方向的一个步骤。它是脱离个人主义的社会和走向公司国家的一个步骤。
第九章职业执照
推翻中世纪行会制度是自由在西方世界兴起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早期步骤。这是自由主义思想胜利的一个征兆,并被广泛地认为确系如此。结果,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在英国、美国以及在较少范围内在欧洲大陆,人们能未经任何政府或类似政府当局的同意而从事他们所企求的任何行业或职业。在最近几十年里,出现了倒退的情况,逐渐有趋势对从事某些特殊职业的个人加以限制,要求由国家机关所颁发的营业执照。
对个人能随意地使用他们资源的自由加以限制就其本身而言也是重要的。此外,他们还提出了不同类型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能应用第一、二章里已经论述过的原则。
我将首先论述一般性的问题,然后是特殊的例子,对开业行医的限制。选择医药的原因为:在这一方面施加限制似乎具有最充分的理由——击倒稻草人得不到多少经验教训。我怀疑,很可能甚至包括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的大多数人相信由国家机关颁发执照来对行医的人施加限制是应该的。我同意:在医药领域颁发执照比在大多数其他领域如此做具有更为充分的理由。虽然如此,我将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在医药领域,自由主义的原则并不能证实颁发执照的正确性,而在医药界由国家机关颁发执照是不可取的。
政府对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限制普遍存在
执照是意义远为一般和范围非常广泛的现象的一个特殊情况。这就是说,法令规定:除了在国家授权机关所规定的条件下,个人不能从事某些特殊的经济活动。中世纪的行会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来表明:一种制度可以明确地规定哪些人能被允许从事于某些特殊的工作。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另一个例子。在等级制度的一定范围内,在行会的较小范围内,实际执行限制的是一般的社会风俗习惯而不是明确地由政府出面。这在较大的程度上适用于种姓制度,而在较小的程度上适用于行会。
关于种姓制度,广泛流传的说法是:每个人的职业完全由他出生的种姓来决定。对一个经济学者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无法设想的制度,因为它规定了个人职业的硬性的分配方式,完全取决于出生率,而根本不考虑需求的条件。当然,这并不是种姓制度的真实情况。真实的情况过去是,而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仍然是:一定数量的不同职业为了某些种姓的成员而被保留下来,但并不是那些种姓的每个成员都从事那些职业。有一些一般性的职业,例如一般的农活,可以为不同种姓的成员所参加。这些提供了调整的办法,不同职业的人的供给适应对他们的劳务的需求。
在目前,关税、公平贸易法、进口限额、生产限额、工会对就业的限制等等是类似现象的例子。在所有这些事例里,政府当局决定某一个人能从事特殊活动的条件,即:允许某些个人与其他人作出安排的条件。这些例子和执照的共同特征为:法律是针对生产者的一方而制定的。以营业执照而言,生产者的一方一般是一个工种。以其他例子而言,它可能是一群生产特殊产品而需要关税保护的人,可能是一群想受到保护以免和“欺骗性的”连锁商店竞争的小零售商,或者可能是一群石油生产者、农民或钢铁工人。
到目前为止,职业执照是非常普遍的。根据我所知道的写了最好的简短调查的沃尔特·盖尔霍恩的说法;“到1952年,除了‘个体经营的业务’,象旅馆和出租汽车公司以此有既多个不同职业已经被法律规定发给执照。除了州的法律以外,有大量市一级的条例规定,更不用说要求执照的职业范围广泛到象无线电操作人员和屠宰场代办商那样的联邦政府一级的法令。早在1938年,单单一个北卡罗来纳州就曾把它的法律规定扩展到60种职业。使药剂师、会计员和牙医象卫生学家、心理学家、成分分析员、建筑师、兽医和图书馆员那样,受到州的要求执照的法律的限制。对这些职业的限制并不使人感到惊奇。但是,当我们听到对打谷机的操作者和碎烟草的商人要求执照时,我们感到多么可笑呢?鸡蛋分等员、驯狗员、消灭害虫的人员、游艇推销员、修剪树木人员、挖井匠、砌砖匠和种植土豆的人,对他们要求执照我们又怎样想呢?在康涅狄格州,对以符合于他们高贵堂皇头衔的严肃性来除去多余和难看的毛发的毛发异处生长治疗人员要求执照。对此,我们又怎么想呢?”在设法说服立法机构制定这类执照要求的争论中,总是把保护公共利益作为辩护的理由。然而,对立法机构颁发职业执照的压力却很少来自曾被有关职业的成员欺骗过或以其他方式胡乱处理过的群众。相反,压力总是来自该职业的成员本身。当然,他们比其他人更知道他们亏待了顾客多少,因而或许他们能够自称为有关问题的专家。
同样,发给执照的安排几乎总是涉及有关执照的行业的成员的控制。当然,在某些意义上,这是十分自然的。假使把水管工的职业限制在具有所需的能力和技巧来为他们的顾客提供良好服务的人,显然只有水管工才能判断谁该发给执照。结果,发给执照的委员会或其他团体几乎总是主要由水管工或药剂师或医生或有关执照发给的特殊职业的成员所组成。
盖尔霍恩指出:“目前在这个国家里,实际在颁发职业执照委员会中的75%完全是由各自职业中的领有执照的开业的人所组成。这些人们,其中大部分只是兼任委员会工作的人员,他们可能在对领取执照者的批准条件和必须遵守的服务标准的内容作出决定时,牵涉到自己的直接的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无例外地直接代表在各项职业范围内的有组织的集体。在通常情况下,他们由这些集体来提名,作为一个由州或其他方面任命的一个步骤。这经常只是一种形式。而形式也常常被免除掉,由职业协会直接任命——例如,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殡葬人员、阿拉巴马州的牙医、维吉尼亚的心理学家、马里兰州的医生和华盛顿州的律师。”
因而,执照的发给往往在实质上不过建立了中世纪行会那种规章制度;在其中,由州把权力赋予专业的成员们。实际上,在决定谁该获得执照时,就一个外行人所能看到的而言,考虑的问题所涉及到的事情往往和专业能力没有任何关系。这并不使人吃惊。假使少数几个人决定其他人是否可以从事一种职业,所有各种无关的条件可能要被加进。至于说会加进什么样的无关的条件,则取决于执照委员会成员的个性和当时的情绪。盖尔霍恩注意到当对共产党颠覆的恐惧遍及全国时各种职业需要的忠诚保证所达到的程度。他写道:“1952年得克萨斯州的法令要求每一个药剂师执照申请人保证‘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或与这个党有联系;对于任何相信或宣传以暴力或非法手段或不合乎宪法的手段推翻美国的集体或组织,他不相信,同时,他既不是任何这种集体或组织的成员,也不支持它们。’这个誓言的一方和宣称用药剂师执照来保护公共保健的利益的另一方之间的联系是很难看出来的。联系更难看出来的是认为有理由要求印第安纳州的专业拳击和摔跤运动员保证他们并没有搞颠覆活动……。由于被证实为是共产党员而被迫辞职的初级中学的音乐老师在哥伦比亚地区不能成为一个钢琴修理匠,因为,他无疑地是‘处在共产党的纪律之下’。华盛顿州的兽医不能医治害病的牛或猫,除非他们首先在非共产党员的保证书上签名。”
不管一个人对共产主义持有什么态度,在规定的条件和执照所企图保证的质量之间的任何关系都是牵强附会的。这些要求的条件所到达的程度有时简直是荒唐的。从盖尔霍恩那里再多引用一些事例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笑料。
最有趣的规章制度之一是给理发师规定的条件。理发师在很多地方是要求执照的一种行业。这里有一个例子来自被马里兰州法庭宣布为无效的规定,虽然在被其他州宣布为合法的规定中能找到类似的语言。“立法通过的规定使法院感到莫明其妙而不是印象良好,因为,这个规定要求新的理发师必须学习下列的课程:‘理发的科学基础、卫生学、细菌学、毛发、皮肤、指甲、肌肉和神经的组织学、头、脸和颈的结构、有关消毒和防腐的基本化学、皮肤、毛发、腺体及指甲的疾病,理发、修面和整容,化妆、着色、漂白和染发.’”再一次引用关于理发师的话:“在1929年,包括在对理发业规章制度的研究中的18个有代表性的州中,没有一个州在那时要求一个愿做理发师的人必须是‘理发学院’的毕业生,虽然所有的州都要求有学徒的期间。今天,同一的各个州的典型的要求是:毕业于不少于(常常超过了)一千小时的如工具消毒那样的‘理论性的科目’然后仍然必须经历一段学徒期间。”我确信:这些引语可以很清楚地表明,发给营业执照并不是国家干预所引起的次要的问题。它们也表明;在这个国家里,国家的干预已经侵犯了个人从事自己选择的活动的自由。它们还表明:随着扩大营业执照的要求对立法机关不断地施加压力,它会成为远为更加严重的问题。
在讨论执照发给的优缺点以前,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为什么执照的发给会存在于现实以及制定这种特殊的规定的趋向可以表明什么样的一般政治问题。很多不同的州的立法机关宣布理发师必须得到由其他理发师所组成的委员会的认可这一事实很难说是一个有力的例证来表明这种立法在实际上对社会有利。应有的解释肯定是不同的,而应有的解释为:在政治上比较容易把力量集中起来的正是生产者的集团,而不是消费者集团。这是经常得到的一个明显的论点,然而这却是一个其重要性不会被过分强调的一个论点。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无论如何,作为生产者的我们比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要远为更加专业化并且使用了远为更多的时间。我们实际上消费着成千上万的不同物品,甚至更多于此。结果,在同一行业里的人,象理发师或医生那样全都对该行业的特殊问题具有强烈的兴趣,并且愿意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于有关该行业的一些活动。另一方面,我们中的那些即使惠顾理发店的人,理发的次数并不太多,在理发店仅花掉我们收入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对理发行业的兴趣是漠不相关的。我们中几乎没有人愿意为了在议会中作出反对限制理发师开业的错误行为而花费很多时间。关税的情况也是如此。认为他们对某一关税具有特殊利益的集团是该关税可以对之发生很大作用的集团。群众的利益是广泛分散的。结果,在没有任何一般的安排来抵消特殊利益的压力的情况下,生产者的集团要比与之不同的、广泛分散的消费者利益的集团对立法机关总是具有远为强烈得多的影响和力量。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确实不是为什么我们有如此之多的愚蠢的发给执照的法规,而是法规为什么不更多。问题是我们如何能有朝一日成功地从我们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对个人生产活动的控制中取得相对的自由。
我能看到的抵御特殊生产者集团的唯一方法是建立一般性的行动原则来反对国家从事某种活动。只有一致公认政府在某一方面的活动应加严格的限制,才能使那些想脱离一般原则的人必须为之而提出足够的强有力的理由,从而有希望来限制为了特殊利益的特殊措施的扩大。这一点正是我们一再谈到的。它的性质和赞成权利法案的性质一样,也和赞成通过规章制度来执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性质一样。
执照引起的政策问题
重要的是要区分三种不同水平的控制:第一,注册;第二,证明;第三,发给执照。
注册。我的所谓注册意思是指一种安排:在其中,假使个人从事于某些活动,他们需要在某种官方登记簿上记下他们的名字。对任何愿意登记他名字的个人,没有任何规定来否定他从事于该种活动的权利。他可能要缴费,或作为登记费,或作为一种税收的办法。
第二是证明。政府机关可以证明某一个人具有某些技能,但决不可以据此而阻止没有这种证明的人从事需要这些技能的活动。一个例子是会计工作。在大多数的州里,任何人都能成为一个会计,不管他是否是一个具有证明书的公共会计师,但是,只有那些通过特别考试的人才能在他们名字后面或在他们的办公室中放上具有证明书的公共会计师的头衔,以便表明:他们是有证明书的公共会计师。证明往往只是一个中间性的办法。在许多州里,趋向是把越来越大的范围的活动限制在有证明书的公共会计师的活动领域之内。就这些活动而言,应该发给执照而不是发给证明书。在某些州里,“建筑师”是一个只能由那些通过一种特殊考试的人使用的头衔。这是证明的情况。这并不妨碍任何其他人从事由于向人们提供如何造房的意见而收取费用的职业。
第三是发给执照。这是一种安排:在其中,个人为了从事某项职业,必须从一个被认可的机关获得一个执照。执照不只是一种形式。它要求表示某些才能或能满足一些旨在于保证才能的测验,而不允许任何没有执照的人开业。同时,如果他开业的话,可以被判处罚款或坐牢。
我要考虑的是这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就有理由来使用这三种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呢?在我看来,有三种不同的理由可以作为使用注册的根据,而同时可不违反自由主义的原则。
首先,注册可以有助于达到其他的目的。让我们举例加以说明。警察往往关心暴力行动。在事件发生以后,应该找出谁有机会接近武器。在事件发生以前,应该不让武器落入可能使用它们于罪恶目的的人之手。要求出售枪支的商店进行注册可以帮助实现上述目的。当然,用早先几章里屡次谈到的论点的意思来说,在某些方面可能具有理由,并不能证明在这些方面存在着理由。有必要根据自由主义的原则来作出一个优缺点的对照表。我现在想说明的意思不过是这一方面的考虑在某些事例中可能具有理由来压倒反对要求人们注册的一般性的行动原则。
第二,注册有时单纯是帮助收税的一个办法。于是,问题变成为某种税收是否是一个适当的方法来提供被认为是必要的政府劳务的资金,以及注册是否助长了赋税的征收。注册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因为,可以向注册的人身上征税,又因为,注册的人可以被用作为赋税的征收人。例如,在收集对各种消费品征收的销售税款时,有必要具备一张出售要征税的物品的单位注册或登记名单。
第三,这是注册的一个可能有的接近于我们主要论点的理由,即:注册可能保护消费者免于受骗。一般说来,自由主义的原则赋予国家强制执行合同的权力,而欺骗涉及违反合同。当然,由于保护消费者免受欺骗本身牵涉到对自愿契约的干预,我们在事先采取保护性的措施时是不能走得太远的。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能以原则的理由来排除这种可能性,即:某些活动很有可能引起诈骗,以致有必要在事先有一张从事这个活动的人的名单。在这一方面,例子之一或许是出租汽车司机的登记。在夜里接客的出租汽车司机可以有特别好的机会去向乘客进行盗窃。为了制止这种行动,有必要具备一张从事出租汽车业务人员的名单,给每个人一个号码,并且要求把这号码放在车上,从而受干扰的任何人只需要记住车子的号码。这仅仅涉及利用警察权力来保护个人不受其他个人的暴力的侵犯,同时也可能是这样做的最方便的方法。
论证证明书的必要性是远为困难的。原因在于这是私人市场一般可以自行完成的。这个问题对产品和对人的劳务来说都是一样的。在很多领域中,存在着私人发给证明书的机构,它们对个人的能力或某一产品的质量给与证明。“好家用品”标记是私人证明的安排。对工业产品而言,有私人试验所对某一产品的质量给与证明。对消费品而言,有消费者试验机构,其中在美国最有名的是消费者联盟和消费者研究所。商业改进局是自愿的组织,它对某些商人的质量出具证明。技术学校和大专院校对它们的毕业生的质量出具证明。零售商和百货公司的作用之一是对他们出售的许多物品的质量给与证明。消费者逐渐对商店产生了信心,而商店又具有动机来通过调查它出售的物品的质量以便赢得信心。
然而,人们可以争辩说,在某些或甚至是在很多事例中,非官方的证明不会被推广到消费者愿意为之而偿付代价的地步,因为,无法使对某一商品的证明不给大家知道。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涉及到专利权和版权的问题,即:个人是否能获得供给其他人服务的价值。假使我从事给人们出具证明的事务,可能不存在有效的方法来要求你为我的证明给与报酬。假使我把我的证明报告卖给一个人,我又怎么能够使他不把我的证明传递给其他人呢?结果,对于出具证明,即使人们愿意为之而支付必要的代价,也不可能达成有效的自愿交换。正象我们解决其他种类的邻近影响一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由政府出具证明。
对证明书的必要性加以论证的另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垄断的存在。在证明书的问题中,存在着一些技术垄断方面的因素,因为,出具证明的代价大部分不取决于能够看到证明的人的数量。然而,这并不能表明,垄断是不可避免的。
以我看来,执照的发给似乎更加难以证明其必要性。它在侵犯个人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的方向走得更远。然而,执照的发给仍然具有一些被自由主义认为是政府应当采取行动的正当的理由,虽然,其中的优点必须总是和缺点来加以权衡。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执照发给的主要的论据是邻近影响的存在。最简单和最明显的例子是可以造成大量疾病的“不合要求的”医生。就他伤害的仅仅是他的病人而言,这只是一个病人和他的医生之间自愿订立合同和交换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没有干预的理由。然而,可以争辩的是:假使医生对他的病人作出错误的处理,他可以造成一切会伤害处于直接交易之外的第三方的大量传染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理解,甚至于包括可能成为病人和医生的人也会愿意把行医的权利限制于“合格的”医生,以免这种大量疾病的发生。
实际上,赞成执照的人所提的主要论点并不是这个有些投合自由主义者的心意的论点,而是一个很少或没有吸引力的纯粹以家长主义的关怀为根据的说法。据这种说法,个人不能适当地选择他们自己的仆人,也不能适当地选择他们自己的医生或水管工或理发师。为了能明智地来选择一个医生,他自己必须是一个医生。据说我们中的很大部分因之而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从而由于无知而必须受到保护。这等于说:作为选民的我们必须保护作为无知的消费者的我们,以便保证人们不受不合格的医生或水管工或理发师的摆布。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举出对注册、发给证明以及发给执照的赞成的论点,在所有三种情况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对其中任何一个有利之处,还必须支付大量的社会代价。这些社会代价中的一部分在上面已被我提出。对医药方面的代价我将比较详细地加以说明,但在这里,把这些代价以一般方式加以论述可能是有益处的。
最明显的社会代价是:不管它是注册、发给证明还是发给执照,这些措施的任何一个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牺牲其他公众利益而取得垄断地位的特殊生产者集团手中的工具。没有办法可以避免这个结果。人们能设计出一套又一套的程序上的控制来防止这个结果,但是没有人可能克服由于生产者的利益比消费者的利益更加集中而引起的问题。最关心于这种安排的人、最迫切要求实施这种安排的人以及最关心于它的管理制度的人会是那些涉及的职业或行业中的人。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施加压力,使得注册扩展为发给证明,使得发给证明扩展为发给执照。一旦发给执照制度得以建立,那些对推翻既定的规章制度感兴趣的人就会被迫而不能施加他们的影响。他们得不到执照,因此必须从事其他职业,从而对推翻既定的规章制度失去兴趣。结果,总是由某一职业的成员们自己对加入该职业的人数加以控制,因而会建立垄断地位。
在这一方面,发给证明的害处较少。假使得到证明的人“滥用”他们特殊的地位,假使在给新加入人出具证明时,该行业的成员提出过分严厉要求,从而过分地减少开业的人数,那末,在有证书和没有证书的人之间的价格差异会大得足以导致公众使用没有证书的开业的人。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对有证书的开业者的劳务的需求具有相当大的弹性,从而有证书的开业者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来剥削其他公众的范围是比较狭窄的。
结果,不发给执照而仅使用证明书是一个折衷的办法,它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使人们免于受到垄断的侵犯。它也有它的缺点,但值得注意的是:通常支持发给执照的论点,尤其是家长主义的论点几乎完全可以由发给证书而得到满足。假使支持发给执照的论点是:我们过于无知,以致不能判断好的开业者,那所需要做的一切便是提供有关的情况介绍。假使完全了解情况而我们仍然要惠顾没有执照的人,那便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不能埋怨我们没有得到情况介绍。由于不属于有关职业的成员的人对发给执照提出的支持论点完全可以通过证书的发给而得到满足,我个人很难找到需要发给执照而不能由发给证书得以满足的任何事例。
甚至于登记也具有相当大的社会代价。它是走向某种制度的第一个重要的步骤: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必须携带身分证,每个人必须在事先通知领导他计划要做的事。此外,象已经表明的那样,登记起于成为取得证书和执照的先声。
行医执照
医疗职业长期以来一向把开业限制于有执照的人。骤然看来,对“我们是否应该让不合格的医生开业呢?”这个问题似乎只能有一个否定的回答。但是,我想指出,稍加思索之后也许会有不同的想法。
首先,发给执照是医疗职业界能对医生的数量进行控制的关键。为了理解这一点,需要对整个医疗职业的结构加以论述。美国医学协会或许是美国最强大的一个工会。工会权力的实质是它能限制从事某一职业的人数的权力。这种限制可以间接地通过实施比通常应有的工资率为高的工资率来实现。假使能够强制实施这种工资率,它会减少能获得工作的人数,因而间接地减少了进入这种职业的人数。这种限制的办法具有缺点。总是会有一批不满现状的人企图进入这项职业。假使工会能直接限制想从事这项职业的人数——总是设法要在其中获得工作的人,它的处境要好得多,把不满和有意见的人一开始便排除在外:这样,工会就不必为他们操心。
美国医学协会正是处在这个地位。它是一个能限制参加人数的工会。它怎么做到这一点?主要的控制是在进入医学院的阶段。美国医学协会的医疗教育和医院理事会对医学院行使批准手续。为了使医学院能够列入被批准的名单之中,它必须符合理事会的标准。在各种不同时期,当减少人数的压力存在时,理事会表现出它的权力。例如,在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医疗教育和医院理事会曾给各个医学院写信,表明医学院招收了比能够按照正规方式给与训练要多的学生。在下一、两年中,每个医学院减少了入学人数,从而提供强有力的例证来表明:它的建议是有些效果的。
为什么理事会的批准会如此重要呢?假使它滥用它的职权,为什么不出现没有被批准的医学院呢?回答是:几乎在美国每一个州,人们必须领得执照才能开业行医,而为了得到执照,他必须是一个被批准了的学校的毕业生。在几乎每一个州里,被批准学校的名单和美国医学协会医疗教育和医院理事会批准的学校名单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发给执照的规定是有效控制入学人数的关键。它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发给执照委员会的成员总是医生,因而在人们申请执照的阶段他们能有所控制。这种控制的有效性要比在医学院一级的控制为小。在几乎所有要求发给执照的职业中人们可以不止一次地申请批准。假使一个人在足够高的级别进行了足够长的时间的申请,他迟早可能达到目的。由于他早已花费了金钱和时间来获得他的职业训练,他有强烈的动机来继续进行。只有对一个受到训练后的人,发给执照的规定才会有效。因此,执照发给的规定主要系通过提高进入某一职业的代价而限制人数,因为,要进入该项职业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又因为不能保证是否会成功。但是,这种提高代价在限制人员进入方面的有效性远远不能和一开始便阻止个人进入该项职业相比拟。假使他在进入医学院阶段被取消掉,他永远不会成为申请人,他永远不会在那个阶段造成麻烦。因此,对某一职业人数控制的有效方法是对进入该职业学校的人数加以控制。
对进入医学院的人数加以控制,然后又对发给执照加以控制能使该职业具有两种限制人数的办法。明显的一种办法是直接拒绝很多申请者。不太明显、但或许更为重要的一种办法是对入学和取得执照设立很高的标准,以致困难到使年轻人丧失勇气不愿进行尝试。虽然大多数的州的法律只要求在进入医学院前完成两年大学课程,但几乎100%的新参加者要完成四年的大学课程。同样,医学训练期限本身也曾加以延长,特别是要求更严格的实习医生的安排。
作为脱离正题的话,在控制进入职业学校这点上,律师从来没有象医生那样取得成功,虽然他们正在向那个方向行进。其中的理由是有趣的。被美国律师协会批准的每一个学校几乎都是全日制学校,而几乎没有一个夜校被批准。另一方面,许多州的议员是法律夜校的毕业生。假使他们投票把进入该职业的人限制为批准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实际上投了他们自己不合格的票。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置身于不合格的行列是主要的因素,趋于对法律界摹仿医学界的成功程度施加限制。多年来,我本人没有从事任何有关进入法律界需要的合格条件这一方面的广泛研究,但我了解,这种限制正在消失。学生具有较宽裕的经济情况意味着较大的一部分的学生将进入全日制法律学校,从而这会改变议员们的学历的比例。
回到医学上来,关于批准学校毕业生的规定是对进入该职业进行控制的最重要的办法。该职业界曾利用这种控制来限制人数。为了避免误会,我要强调指出:我并不是说医学界的领袖们,或负责医疗教育和医院理事会的人故意想尽各种办法来限制人员的进入,以便提高他们自己的收入,那不是事态实际进行的方式。甚至于当这些人明确地谈到限制人数以提高收入的必要性时,他们的辩解理由总是为:假使让“过于多的”人进入该职业,这会降低他们的收入,因此,他们将被迫采用不道德的行医手段来挣得一个“适当的”收入。他们争辩道:维持有道德的行医手段的唯一方法是使人们得到与医生的功用和需要相适应的一定标准的收入。我必须承认,在我看来,根据道德和事实上的理由,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赞同的。医学界的领袖们公开宣布他们和他们的同事们必须得到报酬才能遵守道德是很不寻常的。假使情况确系如此,我怀疑索取的代价是否会有任何限制。看来贫穷和诚实之间并不存在多少正比例的关系,实际情况可能形成相反的比例。不诚实并不总是有利的,但它肯定会有时如此。
只有在象有大量失业和相对低收入的大萧条的时期,才以类似上述的说法来使对人员进入的控制合理化。在平时,使限制成为合理化的说法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说法是医学职业的成员要提高被他们看作为是职业“质量”标准的东西。这种合理化的说法的缺陷是普遍存在的,即:没有真正理解经济制度的运转,也就是说,不能区别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差异。
关于律师的一个事例或许会说明这一点。在一个讨论进入该职业问题的律师会议上,我的一个反对限制进入规定的一个同事使用了汽车行业的一个譬喻。他说:假使汽车行业认为,没有人应该驾驶低质量的汽车,从而不应该允许任何一个汽车制造商生产没有达到高级标准的汽车,这不是荒谬吗。听众中的一个成员站了起来,同意用汽车作为譬喻,并且说:当然,我们这个国家除了使用高质量的律师外,也不敢于使用任何低质量的!这种倾向代表着职业界人氏的态度。他们只看到业务的技术标准,而在实际上的争论是:即使这意味着有些人得不到医疗服务,我们也必须坚持要第一流的医生——虽然他们肯定不会用那种方式来说。然而,人们只应该获得“最优的”医疗服务的观点却总是造成限制性的政策,即:对医生的数目加以限制。我当然不想争辩,认为这是造成限制性政策的唯一原因,但是,却想说明,这种考虑使得很多善良的医生同意于限制性的政策,而如果没有上述的合理化的借口,他们会立即反对的。
不难说明:质量只是一种施加限制的合理化的借口,而不是它的基本原因。美国医学协会的医疗教育和医院理事会的权力曾以某些方式被用来限制人数,而这些方式是完全不可能与质量有关的。其中最简单的例子是他们向各个州建议:应该把公民的资格当作为开业医生的合格的条件之一。我难以想象这和医疗质量有何关系。他们有时企图施加的类似的一个要求是发给执照的考试必须使用英语。关于美国医学协会的权力和权力的有效性质以及关于上述和质量没有关系的论点,我具有一个总是可以突出地说明问题的数字。1933年以后,当希特勒在德国当权时,大量专业人员从德国、奥地利等地外流,当然也包括想在美国开业的医生。在1933年后的五年内允许在美国开业的外国培养的医生数字和在1933年以前五年内的相同。这显然不是事态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些额外医生的威胁导致对外国医生的严格要求,以致向他们施加极重的代价。
可以清楚地看到,发给执照是医学职业能限制开业医生数字的关键。这也是它能限制在行医过程中改变技术和组织的关键。美国医学协会始终反对集体医疗并且反对预先付款的医疗计划。这些行医的方式可能有优点和缺点,但它们代表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自由尝试的技术革新。没有理由可以得出结论,认为行医的最优的技术组织方法是独立开业的医生这一形式。它也可能是集体开业,可能是通过公司组织的形式。我们应该有一种各样方法都能试用的制度。
美国医学协会曾经反对上述的企图,并且一直能够有效地阻止它们。它之所以一直能这么做,因为发给执照间接地使它能对进入医院行医加以控制。医疗教育和医院理事会固然批准医学院,也批准医院。医生要想进入“被批准的”医院行医,他一般得由他所在县的医学协会或由医院委员会批准。为什么不能成立不被批准的医院呢?因为在目前经济条件下,要想使一家医院能正常运行,它必须有实习医生的来源。根据大多数州的发给执照的法规,候补医生要想被准许行医,他必须具有在“被批准的”医院里充任实习医生的经验。“被批准”的医院名单一般是和医疗教育和医院理事会的名单完全一致的。结果发给执照的法律使医学职业控制了医院,也控制了学校。这就是美国医学协会在反对各种不同类型集体医疗上基本上取得成功的关键。在少数事例中,集体医疗能生存下来。在哥伦比亚地区,集体医疗取得了成功,因为它们能够根据联邦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控告美国医学协会,并且赢得诉讼。在其他几个事例里,他们由于特殊的原因曾取得成功。然而,毫无疑问,集体医疗的趋势由于美国医学协会的反对大为放慢。
作为一段有趣和离题的话,我们指出,医学协会只反对一种集体医疗,也就是说,预先付款的集体医疗。其中的经济上的原因看来似乎是:这会消除索取区别对待的价格的可能性。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发给执照处于限制人员进入的核心;它会造成沉重的社会代价,对企图开业行医而不能这样做的个人是如此,对企图购买这种医疗服务而不能这样做的公众也是如此。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执照的发给是否会有据说是它具有好的效果呢?
首先,它是否真正会提高合格的标准?我们完全不清楚,它确实会在该职业的实践中提高了合理的标准,其原因在于下列各点。第一,任何时候当你对进入任何职业设置障碍时,你也就造成了一个回避它的动机,而医学当然并不例外。正骨和按摩职业的兴起并不是和限制进入医学界没有关系。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中的每一种都代表回避限制的企图。这些中的每一种又照例使自己具有执照的规定,从而施加限制。其后果是形成了不同水平和种类的业务,即:区分了医生业务和其替代物,如正骨、推拿、信仰疗法以及其他等等。这些代替物的质量很可能要低于对参与医学界不加限制时的医生业务的质量。
用更加具有普遍意义的话来说,假使医生的数量比没有限制时的数量要少,又假使象一般存在的情况那样,他们的全部时间都已为业务所占用,这使意味着受过训练的医生的开业总额较少——好象是整个医学界具有较少的开业的人时那样。在这种情况下,解决的办法只能是让没有受过医学训练的人开业;开业的人可能完全没有而其中一部分势必没有业务上的合格条件。此外,实际的情况要更为严重得多。假使“医疗业务”应该被限制在有执照的医生,就有必要具体规定医疗业务是什么,而故意设置闲散人员的做法并不是限于铁路行业。根据禁止未经批准的人不能从事医疗业务的法令条文,许多事情被限制在有执照的医生才能从事的范围之内,而这些事情完全可以被技术员或虽未经受过头等的医学训练但却有技术的人妥善地完成。我还没有足够的技术知识来列举出所有的例子。我只知道,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的那些人认为,趋向是要在“医疗业务”中包括越来越多的由技术员可以很好地完成的活动。受过训练的医生把他们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投入于其他人能干得很出色的事情上去。结果是大幅度地减少医疗服务的数量。假使我们能设想出实际医疗平均质量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不能通过对已经提供的医疗服务的质量加以平均而得到,那会象仅仅根据治愈的病人的人数来判断医疗的效果一样。我们还必须考虑施加限制减少了医疗服务的数量这一事实。结果很可能是实际生效的合格程度的平均水平由于限制而减少。
即使上述的评论也并不具有足够的深度,因为,它仅仅考虑了一个时期的情况,而不是不同时期中的变动的情况。任何科学或学术领域中的进展往往来自在专业领域中没有声誉的大批的狂想家和爱好空谈的人的工作的成果。在目前情况的医学专业中,除非你是一个专业的成员,从事研究或试验是非常困难的。假使你是一个专业的成员,并想在专业中处于良好的地位,你所能做的那种试验会受到严格的限制。一个“信念治疗者”可能不过是一个对轻易相信人的病人进行欺骗的一个骗子,但是,或许在其中的一千人或几千人里,有一人会在医学上作出重要的改进。通向知识和学问具有许多不同的道路。对所谓医疗业务施加限制并且象我们经常做的那样把医疗业务局限于某一群人,而这些人基本上必须顺从流行的正统做法。这样做肯定会减少进行试验的数量,从而减少了在这个领域内的知识的增长速度。正如上面已经举出的那样,适用于医学内容的话也适用于医学的组织。我将在下面对这一点进一步加以论述。
发给执照以及与此有关的在医疗业务中存在的垄断也倾向于以另一种方式使医疗的标准降低。我已经指出:它的降低标准可以通过减少医生的数量,可以通过减少受过训练的医生用于较重要的而不是较不重要的任务所使用的总时数,以及可以通过减少研究和发展的动机而出现。此外,它还可以大为增加个人由于治疗不当的事故而向医生索取赔偿时的困难程度并通过这一点使医疗质量降低。保护公民们免受不合格的医生的损害的一个办法是预防受骗以及能在法庭上对治疗不当提出控诉。已经出现了一些控诉案件,而医生们对他们为了治疗不当的保险所支付的高额费用大为埋怨。然而,假使没有医学协会的神经紧张的关怀,对治疗不当的诉讼会比现有的数量更少而且较不容易取得成功。当一个医生可能受到不能在“被批准的”医院中行医的处分时,要想叫另一个医生发表不利于他的证词是非常不容易的。一般说来,证词必须来自医学协会自己所组织的陪审团的成员,而陪审团总是被宣称为维护病人的利益的。
当我们把这些影响考虑在内时,我本人相信,发给执照会减少行医的数量,降低行医的质量,因为,这会减少想做医生的人们所能有的机会,迫使他们谋求被他们认为是具有较少吸引力的职业,又因为,这会迫使公众对较差的医疗服务支付较多的代价;阻碍医学本身和医务组织的技术发展。我的结论是:行医所需的执照应该取消。
在说了所有这一切之后,我怀疑,很多读者会象和我讨论过这些问题的人一样,他们会说;“尽管如此,但是,假使不这样做,我又怎能得到有关医生质量的任何证明呢?即使承认你说的一切关于代价的问题,那末,执照的发给不是能向公众提供某些最低质量的保证的唯一方法吗?”
回答的一部分是:人们现在并不从有执照的医生名单中随意地挑选出一个来;另一部分是:二十年、三十年以前通过考试的能力很难说是目前的质量的保证,因而,执照目前并不是主要的保证,甚至于是最低质量的手段。但是,我们主要的回答是与上很不相同的。主要的答案是:这一问题本身表明了现有的状态对我们的牢固的统治,也表明了:相对于市场的能力而言,在我们所不熟悉的领域中,或者甚至在我们具有一些知识的领域中,我们想象力是如何的贫乏。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推测一下,假使医学专业不行使垄断的权力的话,医学专业将会怎样,质量保证的情况将会怎样。
设想一种情况:在其中,除了由于欺骗和玩忽职守而必须对别人的损害负有法律和财政上的责任以外,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行医,不受任何限制。我推测,整个医学的发展会是大不相同的。目前医疗服务的市场,虽然受到了阻碍,但却可以为不同之处提供一些线索。与医院相并列的集体医疗会大大增长。不象目前的个人开业再加上由政府或慈善机关经营的大医院的体制,可能发展出医疗上的合伙制或公司——即:医疗集体。这些机构会提供集中的诊断和治疗的设施,包括医院的设施。其中某些机构很可能要求预付款项,从而把目前的医院保险、健康保险和集体医疗结合在一起。其他的办法也可以对个别的服务收取个别的费用。当然,大多数机构可能同时使用两种收费的办法。 这些医疗集体——也可被称为医疗百货公司——会是病人和医生之间的媒介。由于它们是长期存在和稳定不变的,它们具有很大的兴趣来建立可靠性和高质量的信誉。由于同样的原因,消费者也会逐渐知道它们的信誉。这些集体会有专业化的技能来判断医生的质量。当它们这样做的时候,它们确实会成为消费者的代理人,正象百货商店现在作为消费者的代理人而判断许多产品一样。此外,它们能有效率地把医疗业务组织起来,把不同程度技术和训练的医务人员结合在一起,使用受过有限训练的技术员来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而把有高度技术和能力的专家保留在只有他们才能完成的任务之中。读者可以根据目前先进的医疗单位的情况,进一步添加更多的内容。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医疗业务都要通过医疗集体来完成。个人诊所会继续下去,正象顾客人数有限的小商店与百货公司同时并存一样,也正象个人法律事务所和大型的合伙法律事务所同时并存一样。医生将建立个人的信誉,而某些病人会喜爱个人诊所的易于保密和私人友谊。某些方面的疾病会由于牵涉的方面很小而不适合于医疗集体来加以治疗,如此等等。
我甚至于不愿意坚持,医疗集体会占有统治地位的说法。我的目的只是想通过例子来说明:除了目前医疗的组织体制以外,存在着很多其他的选择。任何个人或小集体都不可能设想出一切的可能性,更不用说估价它们的有利之处。这种不可能性是一个重大的论据来反对中央政府的计划和反对对进行试验的可能性加以限制的类似专业垄断的安排。在另一方面,支持市场制度的重大论据是它能容纳多样化,它的广泛使用特殊知识和才干的能力。它使特殊集团没有办法来对试验加以阻止,并且使顾客而不是生产者来决定为顾客服务的最好办法。
第十章收入的分配
在这个世纪,至少在西方国家里,集体主义情绪的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相信收入均等构成一个社会的目标,并且愿意使用国家的权力来改进这一目标。在评价这种平均主义的情绪和它所形成的平均主义的措施时,我们必须提出两个很不相同的问题。第一个是规范性的和道德方面的:国家为了促进平等而进行干预的理由是什么?第二个是实证性的和科学方面的:已经采取的措施的效果是什么?
分配的道德标准
在一个自由市场的社会里,收入分配的直接的道德原则是,“按照个人和他拥有的工具所生产的东西进行分配”。甚至运用这个原则也含有依靠国家的行动的意思。财产权是法律问题和社会习俗的问题。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规定它的内容并且加以强制执行是国家的主要作用之一。在充分运用这个原则下的收入和财富的最后分配或许很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所采用的财产法则。
在这个原则和另一个在道德上看来似乎是可取的原则(即:均等待遇的原则)之间具有何种关系?在一定的限度内,这两个原则并不是相互矛盾的。按照产品计酬可能是必要的,以便得到真正的均等待遇。姑且承认,当真存在着能力和财富完全相同的个人,假使其中某些人更加喜爱闲暇,而另一些人更加喜爱在市场上出售的物品,那末,就有必要通过市场所决定的报酬的不平等来得到全部报酬的平等或待遇的平等。一个人可能宁肯要一个一般的工作从而有许多时间可以晒太阳,而不愿有较高工资又要求严格的工作;另一个人可能宁肯和他相反。假使付给两人同样的钱,在较基本的意义上来说,他们的收入会是不平等的。同样,均等的待遇要求干脏而乏味活的人比干美差的人得到较多的报酬。我们所看到的不均等事例的大部分属于这种类型。货币收入的差异抵消了在职业和行当的其他特征方面的差异。用经济学者的术语来说,为了使它们的“差异均等化”,就必须使它们整个金钱上和非金钱上的“净利益”相同。
还需要通过市场的运转而造成的另一种不均等,以便在某些微妙的意义上来造成均等的待遇,或以不同的方式来说,满足人们的爱好。说明这一点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彩票。设想有一群起初具有均等资金的人他们全都同意自愿购买具有很不均等的奖品的彩票。结果所产生的收入的不均等肯定是必要的,以便能使购买彩票的各个人充分利用他们原先的均等地位。如果在事后对收入加以再分配,那就等于否定他们购买彩票的机会。这事例在实际上比按照词义理解“彩票”的概念所表示的情况远为重要。个人部分地根据他们对风险的看法的不同而在各种职业、投资以及类似的东西加以选择。想成为一个电影演员而不是一个政府官员的女子可以说是在故意选择购买一种彩票。在一分钱一股的铀矿股票上投资而不在政府债券上投资的个人也是在如此做。保险是表示不冒风险的程度的一种方法。甚至这些例子并没有完全表明:实际的不均等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能是旨在于满足人们的爱好的安排所造成的结果。这种爱好恰恰对雇用人员和支付报酬的安排施加影响。假使所有可能的电影女演员非常厌恶风险或不肯定性,那末,就会有趋向来发展出电影女演员的“合作社”,其成员事前同意或多或少地来平均分享各自的收入,从而在实际上通过把各自的风险集中在一起而给他们自己提供保险。假使这种爱好非常普遍,那末,把冒风险的和不冒风险的业务大规模地结合在一起的多种经营公司会成为常规的组织形式。碰运气探寻石油的投机家、个人业主制、小规模的合伙经营都会是很稀少的。
确实,这是说明政府通过累进税以及类似的方法进行收入再分配措施的一种方式。我们也可以说:由于某种原因,或许是管理费用,市场不能生产出社会成员所想望的那种形式的彩票或那种类型的彩票,从而累进的税收可以说是一个政府经营的这种业务。我并不怀疑,这个观点包含一些真理。同时,它很难构成为目前的税收辩护的理由。其原因至少在于:目前的税收是在基本上都知道在生活的彩票中谁抽到了奖品和谁抽到了空签以后才施加的,而税收的大部分是由那些认为他们抽了空签的人所制定。按照类似的说法,我们也可以论证:一代人能够为下一代人制定税收方案。推测,任何这种程序至少在纸面上会制定出比目前的累进程度较少的所得税方案。
虽然收入不均等的相当大的部分系来自根据产品而支付的代价,而产品又能反映上述的“差异均等化”或能反映人们对冒风险的爱好程度;但是,收入不均等的很大部分系来自先天的赋予,先天赋予的能力和财产。这是在伦理上真正引起困难的部分。
广泛争论的是:必须区分个人天赋的不均等和个人继承的财产的不均等,以及个人承继的财富的不均等和个人自己获得的财富的不均等。个人能力差异的不均等,或个人自己所累积的财富的不均等被认为是合适的,或至少不象承继的财富的不均等那么明显的不合适。
这种差别是站不住脚的。由于从双亲那里继承到一个为众所喜爱的歌喉而得到高额收益在道德上是否比由于从双亲那里承继到财产而得到高额收益具有任何更大的正当理由呢?苏联人民委员的儿子比农民的儿子肯定能期望得到较高的收入——或许也会期望得到较大的清洗。这是否比美国百万富翁的儿子能期望得到较高收入具有任何一点更大或更小的理由呢?我们能以另一种方式来看同样一个问题。希望把财富传给他的孩子的父母亲能以不同方式来这么做。他能使用一笔款项作为资金把他的孩子培养成为,譬如说,一个有证书的会计师,或为他的工商业的活动打下基础,或建立一项委托基金,使他的孩子有一笔财产收入。在任何这些情况下,这孩子会得到比不如此做为高的收入。但在第一种情况中,他的收入会被看作为来自个人的能力,第二种情况,来自利润,而第三种情况,来自继承的财富。是否有任何道德的基础来在各个收入的范畴之间加以区别?最后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有权得到个人能力所产生的东西,或得到他累积的财富所产生的东西,但却无权把任何财富传给他的孩子们,那似乎是不合逻辑的;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可以使用他的收入于放荡的生活,但却不可以把它传给他的继承人,那似乎也是不合逻辑的。的确,后者也应该是使用他所生产的东西的一个方法。
反对所谓资本主义道德的上述论点不能成立这一事实,当然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道德是可以接受的。我发现,要为接受还是拒绝它寻找理由,或为任何另一种原则寻找理由是很困难的。我逐渐地持有这种观点,即:仅就它本身而论,它不能被当作为一个道德的原则,而它必须被当作为是一种手段或一种原则的后果,例如自由的必然结果。
用一些设想的例子可以说明基本的困难。设想有四个鲁滨逊各自飘流到邻近地区的四个岛屿上去。一个人恰好登上了一个使他生活容易而美好的大而富饶的岛。其他人则登上他们仅能维持生计的小而贫瘠的岛屿。一天,他们发现相互的存在。当然,假使住在大岛上的鲁滨逊邀请其他人参加和分享他的财富,他会是一个慷慨的人。但是,假设他没有这样做。其他三人联合起来并迫使他和他们分享他的财富是否有理呢?很多读者会倾向于说有理。但是,在顺从这种倾向之前,考虑一下在不同形式下的完全相同的情况。假设你和三个朋友沿着街行走,而你恰好看到并且拾到在人行道上的20美元一张的钞票。当然,你会是很慷慨的人,假使你和他们均分这些钱,或者至少请他们喝一盅的话。但是,设想你没有这么做。另外三个人联合起来并迫使你和他们平均分享这20美元是否有理呢?我怀疑,大多数的读者会趋于说没有道理。经过进一步的思考,他们甚至可能认为,上述慷慨的行为方法本身并不显然是“正确的”。我们是否准备劝说我们自己或我们的人类伙伴们,当任何人的财富超过了世界上所有人的平均数时,他便应该立即把多出的数量平均分配给世界上所有的居民呢?当少数人这样做时,我们会羡慕和称赞这个行动。但是,普遍的“分享财富”会使文明世界不能存在。
在任何事态中,两个错误不能造成一个正确。富有的鲁滨逊或那个幸运的找到20美元钞票的人不愿意别人分享他的财富并不能说明别人使用强制手段是有理的。我们能否有理由把我们自己当作我们自己的事件的法官来自行决定:什么时候我们有权使用强制性手段从别人那儿提取我们认为是我们应得的东西呢?或者用强制性手段提取我们认为不是他们应得的东西呢?身分或地位或财富的大部分的差异归根结蒂可以被认为是机会的产物。努力工作和节俭的人会被认为是“该受奖的”;然而,这些品质很大一部分得归功于他幸运地(或不幸运地)所继承到的遗传因子。尽管在口头上比较赞成按“功劳”,而不是按“机会”取得收入,我们却一般地比较易于接受来源于机会的不均等,而不是来源于显然可归因于功劳的不均等。共同事们中彩得奖的大学教授会羡慕他的同事们,但不可能对他们有任何不满之处,或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应有的待遇。假使这些同事的薪水稍有提升,从而使他们的薪水高于该教授自己的,那末,该教授远为更可能会感到不快。因为,机会的女神,象正义的女神一样,毕竟是盲目的。工资的提升是对功劳大小的一个经过考虑后的判断。
根据产品进行分配的有效作用
在一个市场经济中,根据产品计酬的有效作用主要不在于收入分配而在于资源分配。正象在第一章里指出的那样,市场经济的中心原则是通过自愿交换的合作。个人和其他人合作,因为他们能以这种方式更有效地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但是,除非个人得到了他加入到产品中的全部东西,他会根据他能获得的东西,而不是他能生产的东西参与交换,象在每一方都能获得他对产品作出的贡献那样的相互有利的交换不会发生。因此,根据产品计酬是必要的,以便最有效地使用资源。至少在依靠自愿合作的制度下是如此。如果具备足够的知识,就有可能使用强迫的办法来替代取得报酬的动机,虽然我怀疑,其可能性是很小的。人们能把无生命的东西任意支配;人们能强迫个人在某一时间处在某一地方;但是,人们很难迫使个人拿出最大的劲头来。用另一种方式说,用强迫来代替合作会改变可利用的资源的数量。
虽然在市场经济中,根据产品计酬的主要作用是使资源不受强迫而能有效地加以分配,它却不大可能被付诸实施,除非它也被认为能在收入分配上起着符合正义的作用。除非存在着能为社会的大部分成员毫不犹豫地接受的价值判断的基本标准,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是稳定的。某些关键性的制度必须被认为是“绝对的标准”而不只是一种手段。我相信,根据产品计酬曾经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这些大家都接受的价值判断标准或制度之一。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考察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反对者攻击由于按产品计酬而产生的收入分配的理由。社会的价值判断的基本标准的显著特征是它一般地被它的成员所接受,不管他们自认为是该社会制度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甚至资本主义最严厉的内部批评者也暗中承认根据产品计酬在道德上是公道的。
意义最深远的批评系来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争辩说,劳动者受到了剥削。为什么?因为,劳动者生产了整个产品,但却获得了仅为产品的一部分;其余的即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即使我们接受这一论断所包含的对于事实的说明,只有接受资本主义的道德标准,它在价值判断上才能说得通。也只有在劳动者应该获得它所生产的全部东西时,劳动者才是“被剥削的”。假使我们相反地接受社会主义的前提:“各取所需,各尽所能”——不管它可能意味着什么——便有必要把劳动者所生产的不和它获得的东西相比,而和他的“能力”相比,把劳动者所获得的不和它生产的东西相比,而和它的“需要”相比。
当然,根据其他的理由,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也是错误的。首先,在所有合作的资源的总产品和增添的产品——用经济学的术语说,边际产品——之间加以混淆。甚至更为显著的是:从前提到结论中,“劳动”的意义存在着未加说明的改变。马克思承认资本在生产产品上的作用,但把资本当作为物化劳动。因此如果全部写出来的话,那末,马克思主义者的推论的前提会是这样写:“现在和过去的劳动生产了全部产品。现在的劳动只获得产品的一部分。”合乎逻辑的结论应该是:“过去的劳动受到了剥削”,而其在行动上的含义为:过去的劳动应该获得较多的产品。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如何做到这一点,除非是使用精致的墓碑。
达到没有强迫命令而能对资源加以分配是根据产品进行分配的市场经济主要的有效作用。但是,它并不是造成不均等结果的唯一的有效作用。我们在第一章里提到不均等在提供独立的权力中心来抵消政治权力的集中的作用,以及它提供资金的“后盾”来传播不为众所喜的或只是新奇的思想在促进公民自由上所起的作用。此外,在经济领域里,它为新产品的试验和发展提供资金的“后盾”——来购买第一辆实验中的汽车和第一部实验中的电视机,更不用说,印象派的绘画。最后,它使分配能在不需要“权威”的情况下以非个人的方式进行——在没有强制手段的情况下实现合作和协调是市场的一般作用的一个特殊方面。
收入分配的事实
根据产品计酬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够而且在实际上也是具有相当程度的收入和财富不均等的特征。这个事实经常被加以错误的解释,认为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比其他的制度造成更大范围的不均等,从而,作为一个推论,资本主义的扩大和发展意味着不均等的加剧。这种错误的解释又由于发表的大多数收入分配数字令人误解的性质而得以加剧;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不能区别短期和长期的不均等,更是如此。让我们看看关于收入分配一些一般性的事实。
与许多人的期望相反的突出事实之一和收入的来源有关。一个国家越是资本主义化,收入来自被一般认为是资本的部分愈少,而被用来支付给人类劳务的部分愈大。在不发达国家中,如印度、埃及以及其他等等,大约总收入的一半是财产的收入。在美国,大约五分之一是财产收入,而在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比例并不是太不相同。当然,这些国家比不发达国家具有更多的资本。但是,它们在它们居民的生产能力方面甚至更加富有;因此,较大量的来自财产的收入却占有总数的较小部分。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就并不是财产的累积成就,是它为男人和妇女扩大、发展和改进其能力所提供的机会。然而,资本主义的敌人却热衷于申斥它为唯物质的,而它的朋友也往往为资本主义的唯物质主义感到遗憾,并且把唯物质主义当作为进步的必要代价。
另一个与流行的想法相反的突出事实是资本主义比其他的制度造成更少程度的不均等,而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大大地减少不均等的范围。在空间和时间上加以对比都能证实这个观点。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如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法国、英国和美国,肯定比象印度那样的等级社会或象埃及那样的落后国家存在着远为微小的不均等。与象苏联那样的共产主义国家相比则比较困难,因为,例证稀少而且又不可靠。但是,假使以特权阶层和其他阶层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异来衡量不均等,那末,这种不均等在资本主义国家比在共产主义国家里很可能要少得多。仅以西方国家而论,国家愈加资本主义化,在任何意义上的不均等看来是越少:英国少于法国、美国少于英国——虽然这些比较由于考虑到人的内在差异的问题而造成困难。例如,为了进行公正的比较,我们或许不应该把美国不单独与英国本土相比较,而应该和英国本土加上西印度群岛再加上它的非洲领地相比较。
关于时间上的变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所取得的经济上的进展是不均等的大幅度减少。晚至1848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道:“迄今为止(1848年),我们怀疑,已经创造出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类的日常劳动。它们使人口中更多的人同样过着束缚在繁重劳动中的生活,而使更多的制造商和其他人发财致富。它们增加了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但是,它们还未开始对人类命运造成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它们的本性和将来所要完成的。”这种说法甚至对穆勒时代来讲或许也不正确,但是,关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今天,任何人确实不能这样写。对世界的其他各国来讲,这种说法仍然是真实的。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进步和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把人民群众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且使他们可以得到在以前限于上层阶级的产品和劳务,而与此同时,并不以任何相应的方法来扩展富有者所能有的物品和劳务。除了医药以外,技术进展主要只是使广大人民群众具有真正富有者总是能以某种方式得到的奢侈品。我们可以举出几个例子,如现代的供水和排水设备、集中供暖、汽车、电视、无线电。它们给广大群众提供了方便,相当于富有者总是能从仆役、优伶等人中所得到的东西。
以意义明确和能够比较的收入分配形式来表示的这些现象的详细统计例证是难以获得的。虽然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证实了上述的一般结论。然而,这种统计资料可以是非常使人误解的。它们不能把造成均等的和不造成均等的收入的差异分开。例如,棒球运动员的短促的工作寿命意味着在他参加比赛的年份里的年收入肯定要比高于他所能得到的其他职业的收入,以便使棒球在金钱上对他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但是,这个差异对统计数字的影响正和收入的其他的差异一样。收集统计数字时的收入单位的大小也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个人收入的分配总是比家庭单位的收入分配显然具有远为更不均等的程度,因为,很多个人是做零工或获得少量财产收入的家庭妇女或其他同样地位的家庭成员。适用于家庭的收入分配是否应按家庭总收入来对家庭加以划分呢?还是按每人的平均收入来划分呢?或是按每个相应的单位来划分呢?这并不是文字游戏。我相信,按照孩子数目来划分的家庭分配的改变是过去半个世纪里减少这个国家生活水平不均等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比累进的遗传税和所得税远为重要。真正低的生活水平是相对低的家庭收入和相对高的孩子数目的共同产物。孩子的平均数下降,甚至更重要的是,这种下降是伴随着多孩子的家庭的几乎完全消失而到来的,并且主要是由这一原因所造成。结果,就孩子数目而论,现在的家庭倾向于具有更少的差异。然而,这种变化并不会由按照家庭总收入的多少而划分的家庭分配上反映出来。
在解释收入分配数字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需要区分两个基本上不同种类的不均等,即:暂时的、短期收入的差异和长期收入的差异。考虑年收入分配相同的两个社会。在一个社会里,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和变化,从而收入处于特殊等级地位的家庭在年与年之间变动很大。在另一个社会里,存在着很大的固定性质,从而每个家庭年复一年地处于相同的地位。显然,在任何意义上,第二个会是更不均等的社会。一种不均等是动态变化、社会流动性和机会均等的表现;而另一种则是等级社会。这两种不均等的混淆是特别重要的,正是因为竞争的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趋向于用一个来代替另一个,非资本主义社会趋于比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更大程度的不均等;甚至以年收入来衡量也是如此;此外,它们的不均等倾向于不变,而资本主义则破坏身分等级,并且带来社会流动性。
采用政府措施来改变收入分配
政府用来改变收入分配的最广泛使用的方法是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在考虑它们是否有必要之前,值得探询一下,它们是否达到了它们的目的。
根据现有的知识,对这个问题不能给与决定性的回答。下面的论断是我个人的意见,虽然我希望,它不是来自完全无知的意见。为了简便起见,陈述这个意见采取了比例证所能证实的更加肯定的态度。我的印象是:这些税收的措施虽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但它们在缩小用一些统计收入数字来划分家庭的平均地位之间的差异的问题上具有比较小的(虽然不是可以忽视的)影响。虽然如此,在这种已经划分的收入阶层之内,它们实际上在人们之间人为地造成了和上述影响差不多大小的不均等。结果,我们一点也不清楚,按照均等待遇的基本目标或按照收入均等的基本目标来计算的净影响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不均等的程度。
文件上规定的税率看来是高的,而且累进程度也高。但是,它们的影响消失在两个途径之中。第一,它们的一部分影响只是使税收前的分配更为不均等。这是税收通常具有的归宿效果。通过高额税收来阻挠进入高额税收的行业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具有很大的风险和非金钱上的不利之处——它们提高了这些活动的收益。第二,它们造成立法上的和其他的条例来回避税收——所谓赋税法中的“漏洞”,如矿产消耗的比例,免除州和市的债券的利息,对资本收益的特别优惠的处理,虚报实报实销帐目,其他间接的付款方法,把一般收入转换为资本收益以及其他大量的形形色色的办法,其影响在于使真正施加的税率比名义税率低得多,从而,或许是更重要的,使税收的归宿成为不肯定和不均等。处于同一经济水平的人支付很不相同的税款,取决于他们收入来源的偶然性和他们具有的逃税的机会。如果使目前的税率完全有效,那末,对积极性以及与此相类似的影响很可能严重到使社会生产力受到很大的损失。因此,逃税对经济福利可能是必要的。假使如此,那末,得到的福利系以浪费大量资源和造成广泛的不公平为代价。规定一系列较低的税率再加上使一切收入的来源比较平均地纳税的更为全面的征税标准能使赋税的归宿较为累进,使执行的细节较为公平合理,并且使资源遭受较少的浪费。
个人所得税的作用的不肯定的性质,以及它在减少不均等程度上的有限的效果,已经得到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的广泛赞同,包括许多强烈地主张使用累进税来减少不均等的程度的人。他们也极力主张大大减少最高税率并且使纳税标准更加全面。减少累进税对收入和财富不均等的影响的进一步的因素是这些赋税向现有的富人所征收的税款要比向正在成为富人的人所征收的要少得多。虽然它们对使用来自现有财富的收入施加限制,它们甚至更显著地——仅就它们的有效的范围而言——妨碍了财富的累积。对来自财富的收入征税并不对减少财富本身起任何作用,它只是降低消费水平以及减少财富所有者能增添的那部分财富。税收措施减少人们冒风险的积极性并且使他们以较稳定的方式来保存现有的财富,因为,这种方式可以减少现在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消失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累积新财富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从大量目前的收入中储蓄掉一个很大的部分并把它投资于冒风险的活动,其中的一部分会产生高额的收益。假使所得税是有效的,那末,它会关闭这条途径。结果,它的影响会是保护目前拥有财富的人,使他们免于受到新来的人的竞争。实际上,这种影响已经由于上面提到的办法而大部分消失掉。值得注意的是:相当大一部分的新的积累是在石油方面;在那一方面,对矿产消耗比例优待提供了一条特别容易获得免税收入的道路。
在判断累进的所得税的必要性时,以我看来,区别两个问题似乎是很重要的,即使在应用时这种区别不能精确:第一,为了政府决定进行的那些活动(包括如第十二章所论述的消灭贫穷的措施)取得资金;第二,单纯为了再分配的目的而征税。前者很可能要求一些累进的措施,其原因的一部分为应该根据受益的多少而收取代价,另一部分为符合社会的公平合理的标准。但是,目前对高收入和遗产所规定的高额税率是很难以此作为存在的理由的——即使因为它们所能征收到的税款是为数很少的话。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很难看出任何单纯地为了再分配收入而施加累进赋税的理由。这种赋税似乎是一个显著的事例来使用强制手段从某些人那里拿取一些东西,把它们给与别人,因而,和个人自由发生了正面冲突。
把一切考虑在内之后,在我看来,个人所得税的最好的结构是在收入的一定的免税额以上抽取固定比例的税,而其中收入的含义应该非常广泛,并且为赚取收入的开支,规定减免税款的优待办法。正如在第五章提出的那样,我将把上述方案与废除公司所得税相结合,并且要求公司把它们的收入划归股东,同时要求股东把这笔款项计入在他们的纳税是报单据上。最重要的其他有必要的改变是取消石油和其他矿产上的消耗比例的优待、取消对州和地区证券利息的免税、取消对资本收益的特殊处理、把所得税、遗产税和捐赠税加以协调以及取消目前允许的许多纳税优待规定。
我认为,纳税减免额可能是累进的一种合理的办法(在第十二章里将进一步加以论述)。让90%的人口来投票对自己施加赋税并对其他10%的人口规定减免额和90%的人口对其他10%的人口施加惩罚性的税收——实际上,这正是在美国一直在做的事情——是两件迥然不同的事情。按比例的统一收费将使薪金较高的政府工作人员支付较高的绝对额的税款。这从得到的利益来看并不显然是不合适的。然而,这种做法将避免一种任何大多数的人能投票对其他人征收不影响他们自己税收负担的赋税。
用统一税率的所得税来代替目前累进的税率结构的建议会使很多读者认为是一个过分的建议。从名词概念上来看确系如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特别强调指出:从税收的数量上看、从收入的再分配或任何其他有关的标准来看,它并不是过分的。我们目前的所得税纳税率的范围从20%延伸到91%,而对单身汉纳税人的应付所得税的收入超过18000美元,或对填写共同报税单的已婚夫妇应付所得税的收入超过36000 美元的税率高达50%。然而,根据目前所呈报和规定的,即:超过目前免税额并且把目前容许的一切扣除计入以后的应付所得税收入的23.5%这一统一纳税率会征收到和目前高度累进的税率同样多的税款。事实上,即使不去更改赋税法规的其他方面,这种统一的纳税率也会征收到较多的税款,因为,呈报上来的应该纳税的收入的数量会是较多,其原因有三个:会比现在有较少的动机来使用代价昂贵的法律手段来减少所呈报应该纳税的收入的数量(所谓规避税收);会有较少的动机不去呈报在法律上应该呈报的收入(偷税漏税),去掉目前税率结构的抑制积极性的影响会导致更有效的目前资源的使用,从而得到较高的收入。
假使目前高度累进的税率能征收到的税款为数很低,那末,它们对再分配的效果肯定也是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无害的。情况正好相反,能征收到的税款为数很低,因为,这个国家里的一些最有才干的人把他们的精力投入于设计使它保持这么低的办法;也因为很多其他人把纳税的多少当作为一种考虑来决定他们的经济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十足的浪费。我们由此而得到的是什么呢?至多使一些人感到满意,认为国家正在进行收入的再分配。甚至于这种感觉也是建立在对累进税收结构的实际效果的无知之上,而它肯定会消失,假使知道了有关事实的话。
回到收入再分配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明显地存在着与使用赋税来影响收入分配大不相同的正当理由。很大部分的真正的不均等来自市场的不完全性。这些不完全性的许多方面本身就是由政府行动所造成,或者能由政府行动来消除掉。我们有充分理由来调整游戏的规则,以便消除这些不均等的泉源。例如,政府所赋予的特殊垄断特权、关税和其他对特殊集团有利的法律规定都是不均等的泉源,消除掉这些是为自由主义者所欢迎的。推广和扩大教育机会是趋向于减少不均等的一个主要因素。象这样的一些措施具有行动上的优点,因为,它们能击中不均等的泉源而不只是缓和症状。收入的再分配也是一个领域:在其中,政府使用的一套措施所造成的危害大于它使用的另一套措施所能改正的。这是另一个例子来表明:政府把据说是私有企业制度的缺点作为理由来进行干预,而在事实上,许多主张扩大政府职能的人所不满意的现象本身却是政府所造成的,不论其职能是否得到扩大的政府,都是如此。
第十一章社会的福利措施
促成高度累进的所得税的人道主义和平均主义情绪也促成了大批旨在于增加特殊集团的“福利”的其他措施。措施中最重要的一套是一批贴着使人误解的标签的“社会保险”。其他的是公共住房、法定最低工资、对农产品价格的支持、对特殊集团的公费医疗、特别援助方案以及其他等等。
我将首先简要地论述一下后面的几项,主要在于说明:这些项目的实际影响及企图和它们意图的影响之间存在着如何大的不同之处,然后,我将以较多的篇幅来论述社会保险方案中最大的组成部分,老年和人寿保险。
其他次要的福利措施
1.公共住房。经常用来支持公共住房的一个论点是根据被认为是存在的邻近影响:尤其贫民窟地区,在较少的程度上还有其他低质量的住房;据说它们使社会以火警和警察保护的形式支付较高的费用。这种实际的邻近影响可能存在。但是仅就这个影响而言,它所能证明为必要的不是公共住房,而是对这种增加社会费用的公共住房施加较高的赋税,因为,这趋于使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相等。
这会立即引起反驳,认为增加的赋税会落在低收入人们的身上,而这又是不好的事情。这一反驳的真正含意是:建议公共住房的理由不是邻近影响,而是作为帮助低收入人们的手段。假使确系如此,那末,为什么要特别贴补公共住房呢?假使资金是用来帮助穷人,那末,给与现金而不是实物不是更有效的使用资金的方式吗?确实,被帮助的家庭宁肯要一笔现金,而不愿要住房的形式。假使他们希望有住房的话,他们自己可以把钱花在住房上。因此,给他们现金不可能会比给与其他形式的东西更坏;假使他们认为,其他的需要更加重要,那末,给与现金会使他们更加方便。现金补贴可以解决邻近影响的问题以及津贴实物的问题,因为,假使现金不被用来购买住房,它可被用来支付邻近影响所应有的额外税收。
因此,公共住房不能以邻近影响或帮助贫穷家庭为理由。假使有可能为它找出一个理由的话,那末,它只能以家长主义为理由。家长主义的理由是:被帮助的家庭“需要”住房比“需要”其他东西更为迫切,但是,他们自己既不同意这一说法,也不会以明智的方式使用这笔款项。对于合格的成年人而言,自由主义者趋于拒绝这一论点。他不能完全拒绝它的能影响儿童的间接的形式;即:家长们会忽视“需要”更好住房的儿童们的福利。但是,自由主义者在接受作为大笔开支用于公共住房的适当理由的这个最终论点之前,要求比一般所提供的更有说服力和针对性的证明。
在涉及公共住房的实际经验之前,在抽象理论上所能谈论的就是上述这一些。现在,既然我们已经有了经验,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论述。实际上,公共住房已经被证实为具有与它的本意大不相同的影响。
远没有象赞成者所期望的那样改善了穷人的住房问题,公共住房却恰得其反。在建造公共住房计划过程中被拆毁的居住单位的数量,远远超过新建造的居住单位的数量。但是,象这样的公共住房方案却对减少需要居住这种住房的人数不采取任何解决办法。因此,公共住房的作用是提高每一居住单位的人数。有些家庭或许要比没有公共住房时的住房条件要好——是那些运气好到能住进国家建造的住房单位中的人。但是,这不过使其他人的问题更糟,因为,总的平均密度上升了。
当然,私人企业会通过改造目前的和建造新的住房来抵消公共住房的某些有害之处,来容纳直接被排挤掉住房的人,或更一般地来容纳那些在公共住房方案所引起的音乐抢座位游戏中间接或更间接地被排挤掉住房的人。然而,这些私人住房的来源在公共住房计划不存在的情况下也会存在。
为什么公共住房计划具有上述影响呢?由于我们曾经一再强调的一般性原因,推动许多人赞成制订这个方案的一般兴趣是分散的而且并不固定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一旦方案被接受下来,它肯定会被特殊利益所把持。在公共住房的情况下,特殊利益是那些当地的集团,它们渴望把破烂地区加以清除和再建,其原因或由于它们在那里拥有财产,或由于破烂地区正在威胁着当地或市中心商业区。公共住房可用作为一个方便的手段。因为,它要求的拆毁数量大于修建数量。即使如此,从日益增长的要求联邦政府资金解决问题的压力来看,“城市的破烂”仍然以不减少的规模在我们社会中存在。
赞成公共住房的人希望从它获得的另一个好处是通过改善住房条件来减少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在这里,很多方案的事例再一次表明恰好相反的影响,除了它完全不能改善平均的住房条件以外。由于对以补贴租金住进公共住房的人的收入施加应有的限制,“破裂”的家庭高密度地集中在一起——特别是,带着孩子的离了婚的母亲或寡居的母亲。破裂家庭的儿童特别可能成为“有问题”的儿童,而这些儿童的高度集中很可能增加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其中一个现象是:公共住房区域对邻近各个学校所起的不利影响。一个学校虽然容易吸收少量“有问题”的儿童,但是,它要吸收大量的这类儿童却是很困难的。然而,在某些事例中,破裂的家庭占有整个公共住房地区的三分之一或者更多,而这个地区的儿童可能占有一个学校中的大部分。假使这些家庭能通过现金补助得到支援,那末,它们一定会在整个社会内分散得更开。
2.最低工资法。最低工资法也许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其影响和善意支持该法规人们的意图恰好相反的最明显事例。很多赞成最低工资法的人们对特别低的工资率表示痛惜是完全应该的:他们把它当作为贫穷的一个征兆,而他们希望通过法律来禁止低于某种特殊水平的工资以便减少贫穷。事实上,如果最低工资法有任何影响的话,那末,它们的影响显然是增加贫穷。国家能够通过立法制订一个最低工资率。但它很难要求雇主按照最低工资雇用所有以前在最低工资率以下被雇用的人。这样做显然是不符合雇主利益的。因此,最低工资的影响是使失业人数多于没有最低工资时的情况。就低工资率确实是贫穷的象征而言,那些因之而失业的人们恰恰是那些最经受不起放弃他们一直在拿收入的人,虽然这笔收入对投票赞成最低工资的人们来看似乎数目很小。
这个事例的一个方面很象公共住房的事例。在两个事例中,受帮助的人是看得见的——是工资被提升的人,以及住进公共住房单位的人。其中受到损害的人是看不见的,而他们的问题并不显然与问题的原因发失联系:那些参加失业行列的人,或更可能的情况是,由于最低工资的存在而从来未能在某些职业中受到雇用的人,他们被迫接受甚至报酬还要低的工作或进入救济的人群;那些更紧密地拥挤在各个贫民窟里的人,他们看来似乎是需要更多公共住房的象征,而不是现有的公共住房造成的后果。对最低工资法很大一部分的支持不是来自与自身利益无关的善意的人,而是来自与自身利益有关的派别。例如,北方工会和受到南方竞争威胁的北方厂商赞成最低工资法来减少来自南方的竞争。
3.农产品价格的支持。对农产品价格的支持是另一个例子。除了在选举机关和议会中农村地区的代表过多这一政治事实以外,如果要想找出任何支持农产品价格的理由,那末,我们只能相信,农民们平均说来具有低收入。即使这一点作为事实被接受下来,农产品价格的支持也并没有完成帮助需要帮助的农民这一意图。首先,假使存在着任何好处的话,那末,好处与需要恰成反比,因为,好处是和市场上出售的量成比例的。贫穷的农民不仅在市场上比富有的农民出售得更少;除此以外,他还从为自己生产的物品中获得较大部分的收入,而这些部分并不能获得价格支持的好处。其次,假使有任何好处的话,那末,农民从价格支持方案中所获得的好处比支出的费用的总量要少得多。这显然适用于储藏仓库和类似的费用,因为,它们是农民根本拿不到的——实际上,储藏仓库和设备的供应者很可能是主要的受益者。这同样也适用于用来购买农产品的费用。因为,这会诱使农民把额外的款项用于肥料、种子、机械等上面。至多,只有多余部分才能加进他的收入项目之内。最后,甚至这个额外的多余部分也夸大了好处,因为,由于支持方案的影响,农村中的农民比没有价格支持时要多。只有在价格支持方案下农民们的所得超过他们不在农场工作时的所得的部分,如果这一部分存在的话,它才构成农民净得的好处。农产品收购方案的主要影响只是使农业的产量更多,而不是提高农民的平均收入。
农产品收购方案的一些代价是如此一目了然和众所周知,以致只需要稍提一下:消费者要付两次款:一次是为支持方案的费用而缴纳税款,还有一次是为了购买食物要支付更高的价标。农民被繁琐的限制和具体的集中控制所束缚,而国家则被扩大了的官僚体制所捆住。然而,还有一系列大家不太知道的代价。农产品价格支持方案是执行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障碍。为了维持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的国内价格,就有必要对许多项目的进口施加限额。我们政策中反复无常的变化,曾经对其他国家具有严重的不利影响。高价棉花促使其他国家扩大它们的棉花产量。当我们的高价导致庞大的棉花存量时,我们开始以低价向海外出售,从而使那些受到我们的影响而扩大产量的生产者遭受严重损失。类似情况还可以举出很多。
老年和遗族保险
“社会保险”方案是维持现状的暴政开始发生魔力的那些东西之一。尽管它在开始时具有争论,它已逐渐被认为是既成的事实并且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对它的必要性不再有所怀疑。然而,它涉及大规模地侵犯国家大部分人的个人生活,就我所知,不存在所以这样做的有说服力的理由。这不仅在自由主义者的原则上,而且在几乎任何其他的原则上都是如此。我将考察这一方案的最大的方面,即:牵涉到向老年人的支付款项的方面。
作为一个实施的项目,被称为老年和遗族保险的方案包括加在工资额上的一种特殊税收再加上对已经到达一定年龄的人支付款项,其数量取决于开始支付时的年龄、家庭的情况以及过去的收入的大小。
作为一个被分析的项目,老年和遗族保险包括三个可以分解的部分:
1.要求广大阶层的人们必须购买被具体规定的养老金,即:对老年时期的生活来源作强制性的准备。
2.要求必须从政府那儿购买养老金,即:提供这些养老金机构的国有化。
3.是一个收入再分配的办法,其原因在于:参加这个系统的人所应得到的养老金的金额并不等于他们将为之而缴纳的税款。
显然,没有必要把这些部分合併起来。可以要求个人支付自己的养老金;可以允许个人从私人公司购买养老金;同时可以要求个人购买具体规定的养老金。政府也可以从事出售养老金的事务而又不强迫个人购买具体规定的养老金,并且要求这项事务收支相抵。此外,政府显然能够并且已经从事于收入的再分配而不需要使用养老金的办法。
因此,我们依次考虑这些部分,以便探求:假使它们的存在是具有理由的话,那末,其理由是什么。我认为,如果我们把它们的顺序颠倒过来加以考虑,那会使我们的分析较为方便。
1.收入再分配。目前的老年和遗族保险方案涉及两种主要的再分配:一种是从该方案的受益者到其他受益者的再分配,另一种是从一般纳税人到该方案的受益者的再分配。
第一种再分配主要是从那些比较年轻时参加该方案的人到那些年龄较大时参加该方案的人。后者目前和在将来的一段时期中得到比他们缴付的税款所能购买的为多的利益。另一方面,按照目前税收及利益的规定,那些在年轻时参加该方案的人所得到的肯定要较少。
我看不出任何理由——自由主义者的或其他的——可以用作为这个特殊的再分配的根据。对受益者的补助和他们的贫穷或富有没有关系:有钱的人获得的补助和贫穷的人一样多。用作补助的税是一种在一定定额下对收入所征的统一税率的税。它在低收入中比在高收入中占有较大的部分。有什么样的可以设想出的理由来要求青年人负担老年人的补助金,而不论老年人的经济情况如何?有什么理由为此而对低收入而不是高收入的人施加较高的税率,或者来为此而对工资抽税以便提高预算收入得以支付补助金呢?
第二种再分配的产生是因为这个养老金机构不可能完全收支相抵。在许多人参加并且缴纳税款而很少人有资格获得利益的时期,这个机构似乎是收支相抵的,而且确实还会有盈余。但是,这种表面现象忽视了正在累积起来的应支付给目前纳税的人的债务。我们怀疑,缴纳的税款是否足以偿付累积起来的债务。许多专家宣称,即使以现金的收支而论,也需要加以津贴。这种津贴在其他国家相类似的机构中一般总是必要的。这是一个高度技术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加以深入的论述,而关于这个问题,可能存在着真正不同的意见。
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只需要提出一个设想出的问题,即:假使有必要的话,从一般纳税人那里把津贴取来是否是有道理的。我看这样做是没有理由的。我们也许愿意帮助穷人。是否有理由来帮助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而只因为他们恰好处于一定大小的年龄呢?这不是一个毫无原则的再分配吗?
我所碰到的涉及该方案的再分配的唯一论点是一个我认为完全不道德的论点,尽管该论点得到广泛的使用。这个论点是:该方案的再分配平均说来是帮助低工资的人多于帮助高工资的人,尽管其中具有很大程度的无原则的因素;如果能更有效地来进行再分配,那当然更好;但是,公众不会直接投票赞成这种再分配,虽然它会投票赞成作为社会保险的一揽子方案中的一部分。在实质上,这个论点说的是:把某一措施的真意掩盖起来,公众可以受到愚弄来投票赞成为他们所反对的这个措施。不用说,以这种方式争辩的人在他们谴责“不真实的”商业广告中声音最大!
2.对提供所要求的养老金的机构国有化。假设我们要求每人支付他所得到的养老金以便避免收入的再分配。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是:把死亡和利息收益考虑在内,保险费等于养老金的现在值。这样,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人们从政府企业那儿购买养老金呢?假使收入再分配是需要完成的目标,那末,显然必须使用政府收税的能力。但是,假使收入再分配与本方案无关,而正象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也很难找出使之成为本方案的一部分的任何理由,那末,为什么不允许希望这样做的个人从私人企业那儿去购买他们的养老金呢?一个很相近的例子是:各州强制要求购买汽车事故保险的法律。就我所知,没有一个具有这样法律的州甚至有一个由州经营的保险公司,更不用说强制汽车主从政府机构去购买他们的保险了。
可能有的大规模的经济效果不能构成理由来使养老金机构国有化。假使存在着大规模的经济效果,而政府又建立一个公司出售养老金的契约,那末,它可能由于自己的规模而以低于竞争者的价格出售。在那种情况下,它将不需要强制性的规定而能具有市场。假使它不能以较低的价格出售这些契约,那末我们有理由相信,大规模的经济效果是不存在的,或是不足以抵消政府经营的不经济之处。
养老金机构国有化的一个可能的优点是有助于强制执行养老金的购买。然而,这似乎是一个相当微小的优点。要想找到一个功用和它相同的行政上的安排并不困难。例如,要求个人在呈交他们的所得税呈报单的同时,包括一份支付养老金的收据,或者让他们的雇主出具证明,说他们已经满足了这一要求。这种行政上的问题,与目前的安排上所造成的问题相比肯定会是次要的。
国有化的代价似乎显然要超过它的任何微小的优点。在这里,象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个人的自由选择和私人企业争取顾客的竞争会促进现有的各种养老金契约的改善,以及增加各种多样化和差别性以便满足个人的需要。在政治方面来看,避免政府活动规模的扩大以及每一次这种扩大给自由带来的间接威胁其有显著的好处。
一些不太显著的政治代价来自目前方案的性质。其中涉及的问题具有很大的技术性和复杂性,外行人往往没有条件来判断它们。国有化意味着大量的“专家”成为国营制度的雇员,或者大学中的人们与它紧密地联系起来。不可避免的,他们逐渐赞成它的扩大,我必须立即指出:其原因并不在于狭窄的自身的利益,而在于政府的行政管理已经被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且他们仅仅熟悉如此条件下的技术方面的知识。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唯一优越之处是存在着从事类似业务的私人保险公司。
议会对象社会保险局这样的机构的业务进行有效的控制,由于它的任务的技术性质和它对专家的接近于完全的垄断的结果,在本质上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它们成为自治的机构,其建议总的说来是由议会全盘接受。在这些机构中的那些能干和有野心的人自然渴望扩展他们机构的职权,而要想阻止他们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假使专家们说“是”,又有谁能说“否”呢?因此,我们看到日益增长的比例的人口被拖入社会保险系统,而现在,向那个方向扩展已经没有多少可能性。于是,我们看到增加新方案的趋向,如公费医疗。
我的结论是:反对养老金机构国有化的论点是十分有力的,不仅按自由主义的原则而论,而且甚至按福利国家的支持者的价值观来看,也是如此。假使他们相信,政府能比市场提供更好的业务,那末,他们应该赞成政府企业与其他私人企业在举办养老金上进行公开的竞争。假使他们是正确的,那末,政府企业会兴旺起来。假使他们错了,那末,人们的福利会由于有私人的机构而得以提高。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言,只有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为了集中控制本身而相信它的人,才能采取赞成养老金机构国有化这个原则立场。
3.强制购买养老金。在排除了枝节问题之后,我们现在准备面对主要的问题,即:强制个人使用他们目前的一部分收入来购买养老金为他们的老年作准备。行使这种强迫性的一个可能的理由纯粹是家长主义的。假使人们愿意的话,他们可能单独地去做法律要求他们作为一个集体而去做的事情。但是,当他们单独行动时,他们目光短浅并且不为将来着想。“我们”比“他们”头脑清醒,知道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应该在比他们自愿做时更努力来为他们的老年作准备;我们不能个别地来说服他们;但是,我们能够说服51%或者更多的人去强迫所有的人去做对他们自己有好处的事。这种家长主义是对正常的人使用的,因此,甚至不需要象关心儿童和疯子那样的借口。
这种观点在内部是一致的和合乎逻辑的。相信这个观点的彻底的家长主义者不会由于向他指出在逻辑上的错误而受到劝阻。他是我们在原则上的反对者,并不仅是一个善意而误解的朋友。基本上,他相信独裁,仁爱的独裁,并且还可能是多数主义者,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相信独裁。
我们这些相信自由的人会必然相信个人自己犯错误的自由。假使有人故意喜欢为今日而生活,喜欢为了目前的享乐而使用他的财富,故意选择一个贫穷的老年,那末,我们有什么权利来阻止他这样做呢?我们可以与他争论,设法劝说他,说他是错误的,但是,我们是否有权使用强迫手段来阻止他去做他选择要做的事呢?是否总是存在着他是正确而我们是错误的可能性?谦虚是相信自由的人的显著美德,而骄傲则是家长主义者的。
很少有人是彻底的家长主义者。假使用今天的眼光加以冷静的考察,它是很不使人感兴趣的观点。然而,家长主义的论点曾在象社会保险那样的措施上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以致似乎值得把它明确地加以论述。
根据自由主义者的原则,强制购买养老金的可能的理由之一是,不为将来打算的人不会遭受他们自己行动的后果,但却使别人担负代价。据说我们不会愿意看到贫困的老年人忍受贫困的生活。我们将通过私人和公众的慈善事业来支援他们。因此,不为老年作准备的人会成为公众的负担。强制他去购买养老金是有理由的,其原因不在于他自己得到的好处,而是为了我们其他人得到的好处。
这个论点的份量显然取决于事实。假使90%的人口在没有强制购买养老金的情况下,会在65岁时成为公众的负担,那末,这个论点会有很大的份量。假使只有1%会成为公众的负担,那末,这个论点就没有份量。为什么为了避免1%的人施加于社会的负担,要限制99%的人的自由呢?认为如果不强制购买养老金,社会的大部分会成为公共负担的想法来源于老年和遗族保险方案成立的时候,即:来源于那次大萧条。从1931年到1940年,超过七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年纪较大的劳动者的失业比例则较高。这种经验是史无前例的,而迄今也没有重复发生过。它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人们不为将来着想、不为老年作好准备。正象我们曾经看到的那样,这是政府管理不当的后果。假使该方案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话,那末,它是解决一种非常不同的问题的办法,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经验。
三十年代的失业肯定在救济贫困的人、在救济许多成为社会的负担的人上造成了严重问题。但是,年纪大决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很多有劳动能力的人是处于救济和支援的名册之中。随着该方案的不断扩大,直到今天已有一亿六千万以上的人接受救济金,而它并没有阻止接受公共支援人数的不断增长。
对老年人照顾的私人安排随着时间的变动而大大改变。在一段时期中,子女是人们为他们自己老年作好准备的一个主要手段。当社会变为更加富裕时,富裕的社会改变了它的做法。加在子女身上要照顾他们双亲的责任下降,而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以累积财产或私人养老金的形式为老年作准备。最近,超过该法案规定数额以外的养老金计划迅速发展。确实,有些学者相信,目前不断发展的趋势指向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很大一部分的人在他们能工作的年月里尽量俭省,以便为他们自己的老年提供比他们在青春时代享受过的要高的生活水平。我们有些人可能认为,这种趋势是不健康的,但是,假使它反映了社会的爱好,那末,也只有听任它如此。
因此,强制购买养老金为了很少的好处而花费很大的代价。它剥夺了我们对我们相当大部分的收入的控制,要求我们把它用于特殊目的,即:以特殊方式从政府机构那里购买退休养老金。它阻止了出售养老金和发展退休安排的竞争。它造成了巨大的官僚机构,而这种官僚机构靠着它自己的扩大而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向,把它的范围从我们生活的一个领域延伸到另一领域。所有这一切是为了避免很少的人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危险。
第十二章贫穷的减轻
从绝对的意义来说,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西方国家所经历的非凡的经济增长和自由企业的利益的广泛分配大大减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贫穷的程度。但是,在部分意义上,贫穷是一个相对的问题,甚至在这些国家里,显然存在着很多人生活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所认为的这种贫穷之中。
一个解决途径,而在许多方面还是最理想的途径便是私人慈善事业。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由放任主义的全盛时期,即:英国和美国十九世纪之中期和晚期,我们能看到私人慈善机构和组织的急剧增加。政府福利活动扩展的主要代价之一便是私人慈善活动的相应下降。
人们可能争辩,私人慈善机构是不够的,因为,从其中获得利益的人不是那些向慈善机关捐赠的人——再一次构成一种邻近影响。当我看到贫困,我感到不快;由于它的减少我得到好处;但是,不管是我还是别的人为了减少贫困而支付费用,我都得到相同的好处;因此,我部分地获得了其他人慈善行为的好处。用不同的话来说,我们大家可能都愿意帮助救济贫困,假使其他人也是如此的话。如果没有这种担保,那末,我们可能不愿意捐赠出同样的数量。在小的集体里,公共的压力甚至在私人的慈善事业中也能足以实现上述保证。在逐渐成为我们社会的主要形式的大的非个人集体里,要想做到这一点困难得多。
假设象我那样,我们接受了这种道理,把它当作为政府采取行动来减少贫穷的理由,这好象在社会中的每个人生活水平之下规定了一个最低限度。现在,仍然留下的问题是规定的高低究竟是多少以及如何去规定它。我看不出决定“高低为多少”的办法,除非根据我们——我的意思指我们大部分人——愿意为此目的而施加于自己的赋税数量。“如何去规定”的问题具有较大的推测的余地。
有两件事情似乎是清楚的。首先,假使目的是减少贫困,那末,我们应该有一个旨在于帮助贫苦人的方案。我们有各种理由来帮助恰好是一个农民的穷人;帮助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是农民,而是因为他贫穷。这就是说,该方案的目的应该是帮助作为一般人的人,而不是作为特殊职业集团中的人、或不同年龄的集团中的人、或某种工资率的集团中的人、或劳动组织或行业成员中的人。这是农业方案、一般老年人的救济金、最低工资法、偏袒工会的法律、关税、某种工种或职业领取执照的规定等等似乎无穷尽的事例中的一个缺点。第二,只要有可能,该方案在通过市场发生作用时,应该不妨碍市场正常状态或不阻碍它的正常作用。这是农产品价格支持、最低工资法、关税以及类似事项的一个缺点。
从纯粹的执行机制的理由上看,应该建设的安排是一种负所得税。按照联邦所得税的规定,我们现在每人收入600 美元可以不纳税(加上最低限度10%的统一扣除)。假使一人得到100美元应纳税的收入,即:超过免税和扣除的100美元收入,那末,他得纳税。按照负所得税的建议,假使他的应纳税的收入为负数值的100美元,即:比免税加上扣除的总额少100美元,那末,他得纳付负数值的税,也就是,得到一笔津贴。例如,假使津贴的比例是50%,那末,他将获得50美元。假使他一点也没有收入,并且为了简单化起见,没有扣除额,而税率仍然不变,那末,他将获得300美元。假使他有扣除,他可能获得的比这个数量还要多。例如,医疗费用,从而,甚至在减去免税额以前,他的收入减去扣除以后是负数。津贴的百分比当然可以是累进的,正象超出免税额的税率那样。以这种方式,可以规定一个任何人的净收入(现在的定义包括津贴在内)都不会低于这一最低限度——在上述简单的例子中是每人300美元。规定具体的最低限度将取决于社会是否有负担的能力。
这一安排具有明确的好处。它是专门针对贫穷问题的。它向个人提供最有用的形式的帮助,即:现金。它是一般性的,从而能代替现在已经实施的很多的特殊措施。它明白地表示出社会所负担的费用。它在市场之外发生作用。象任何其他缓和贫穷的措施那样,它减少那些被帮助的人的帮助他们自己的动机,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消除那种动机,正象任何对收入津贴到某一固定的最低额的制度一样,额外赚取的一美元收入总是意味着更多的可以使用的款项。
毫无疑问,会有行政管理问题,但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似乎是一种次要的缺点,如果它们能被算作为缺点的话。这个制度能够配合我们目前所得税制度,并能与之连在一起加以管理。目前的税收制度包括大部分得到收入的人,把所有的得到收入的人都包括在其中必然会作为副产品而改善目前所得税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假使它能付诸实施来代替目前指向同一目标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措施,那末,整个行政管理的工作肯定会减轻。
几个简单的计算结果也表明:这个建议在费用方面远为要小,更不用说它所牵涉到的政府干预的程度少于我们目前所采用的一系列的福利措施。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这些计算结果可以被用来表明:作为帮助穷人的措施而论,我们目前的措施是多么的浪费。
1961年,政府在直接的福利和各项方案上的开支大致为330亿美元(联邦、州和地区)包括:对老年人的援助、社会保险金额的支付、对不能独立生活儿童的援助、一般性的援助、农产品价格支持方案、公共房屋,等等。在进行计算时,就排除了对退伍军人的照顾。我也没有计入下列措施的直接和间接的费用,如最低工资法、关税、执照规定,等等,以及没有计入公共卫生活动、州和地方在医院、精神病院以及类似的方面所花费的费用。
在美国大约有57000000个消费单位(独自生活的个人和家庭)。如果把1961年的330亿美元的开支以单纯的现款津贴发放,那末就可以发给最低收入的10%的消费单位,每单位几乎为6000美元。这种津贴将会提高它们的收入,使它超过美国所有单位的平均数。换言之,这些开支将会向最低收入的20%的消费单位发放每单位几乎为3000美元的津贴。即使我们同意新政派人士喜欢称之为三分之一的人营养不好、住房不好和衣着不好的说法,1961年的开支也会向每个消费单位发放几乎为2000美元的津贴。这个数字大致是经过物价水平调整以后的三十年代中期三分之二高薪和三分之一低薪的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今天,经过物价水平调整以后,少于八分之一的消费单位具有象三十年代中期最低三分之一人那样的收入。
显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比“减轻贫穷”的字眼所能容许的要远为奢华的方案,即使我们以相当松散的意义解释这个名词的话。如果执行一个补充收入最低的20%消费单位的收入的方案,使它们的收入达到比它们高的收入的最低水平,那末,该方案的费用少于我们现在花费的一半。
所建议的负所得税的主要缺点是它的政治含意。它建立了一种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对某些人施加赋税来津贴其他人。可以设想,这些其他人是有选举权的。总是会存在着那种危险,即:它不是成为绝大多数人愿意给他们自己施加赋税来帮助不幸的少数的安排,而是相反地被转变为一种大多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不同意的少数人身上施加的赋税。由于这一建议使这个过程如此明确,上述危险或许要大于其他措施的危险。除非依赖于选民的自我克制和良好愿望,我看不出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1914年迪赛在一个相应的问题——英国的老年退休金——上写道:“有见识的和仁慈的人很可能要问自己,英国作为一个整体是否会从制订一个法令中得到好处。该法令规定:以老年退休金的形式来领取贫穷救济并不和保持选举议员的权利发生冲突。”
关于迪赛的问题,从英国的经验所得到的结论到目前为止必须认为是不肯定的。英国确实是走向普选权,而并没有取消领取养老金的人或其他接受国家援助的人的选举权利。也存在着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对一部分人的赋税的大量增加。这些税收肯定可以被看作为阻碍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因此,甚至于对那些把自己看作是接受救济的人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好处。但是,这些措施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毁坏英国的自由或它的主要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选民们想逆转潮流和实施自我克制的一些迹象。
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是相信个人的尊严,相信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机会充分利用自己的能力和机会,但条件是他不干涉其他人做同样事情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对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信念;在另一种意义上,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信念。每个人都有得到自由的平等权利。这是一个重要和基本的权利。正是因为人们是不相同的:因此,一个人会比另一个人愿意用他的自由来做不同的事情,而在这个过程中,他能够比另一个人对许多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一般文化作出更多的贡献。
因此,自由主义者在一方面会严格区别均等权利和均等机会,而另一方面,严格区别物质的均等或成果的均等。他可能欢迎自由社会迄今比任何其他社会趋于具有更多的物质的均等这一事实。但是,他会把它看作为自由社会的合乎理想的副产品之一,而不是它存在的主要理由。他将欢迎既促进自由又促进均等的措施——如消除垄断权力和改善市场运转的措施。他将把旨在于帮助较不幸的人的私人慈善行为看作为正确使用自由的一个例子。他可能赞成国家对改善贫穷而采取的行动看作为社会大多数人能达到一个共同目标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然而,他这样做时会感到遗憾,因为,必须使用强制的手段来代替自愿的手段。
均等主义者也会走得这样远。但是他会走得更远。他会为取自某些人来给与其他人的行动进行辩护,不把这一行动当作为“某些人”能够达到他们所想要达到的目标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而是把“公正”当作为辩护的理由。在这一点上,均等显然与自由发生冲突。我们必须加以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可能既是均等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
第十三章结论
在二十和三十年代,美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到说服,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妨碍经济繁荣、从而妨碍自由的不良的制度,并且认为,未来的希望在于政治当局对经济事务进行较大程度的人为控制。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并不是由于任何实际的集体主义社会的例子,虽然这种转变无疑地系由于苏联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对这个社会的光明的希望而大大加速。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是通过把既存的具有其一切不公正与缺陷的制度和在设想中可能存在的制度加以比较而完成的。进行比较的是实际的情况和理想的情况。
除此以外,在那个时候所能做到的并不多。当然,人类已经经历过许多时期的集中控制和由国家具体地对经济事务加以干预。但是,在政治、科学和技术方面曾经有过革命。人们在当时进行争辩,认为我们使用民主政治结构,现代工具和现代科学会比早先所可能做到的要好得多。
那个时候的态度仍然存在于我们之中。现在仍然具有一种倾向,把任何既存的政府干预看作为应该做的事,把所有坏事归因于市场并且把政府进行控制的建议按照它们理想的形式来加以评价,因为,假使这些建设系由不受特殊利益集团压力的能干的和公正的人们所执行,那末,这些建议是可以产生效果的。主张限制政府的作用和主张自由企业的人仍然处于消极的捍卫他们观点的状态。 然而,条件已经起了变化。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几十年政府干预的经验。不再有必要把实际运行的市场情况和理想的政府干预可能有的情况加以比较。我们能把实际情况与实际情况相对比。
假使我们这样做的话,那末,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的实际运行和它的理想的运行之间的差异——虽然无疑是很大的——与政府干预的实际效果和它意图中的效果之间的差异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现在,谁能在支配苏联一切的大量暴政和专制下看到推进人类自由和尊严的任何巨大的希望呢?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着:“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在今天,谁能认为苏联的无产者的锁链比美国的、或英国的、或法国的、或德国的、或任何其他西方国家的无产者的锁链要轻一些呢?
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看一下国内的情况。在过去几十年中,假使有任何巨大的“改革”达到了它的目标的话,那是哪一个呢?这些改革的建议者的良好意图已经实现了吗?
为了保护消费者而对铁路设置规章制度很快成为一种工具:据此,铁路便能保护自己免受新出现的对手的竞争——当然,其中受害的是消费者。
起初以低的税率来制订、以后又被当作为使低收入阶层受惠的收入再分配的一个手段的所得税,已经变成了一个虚有其表的东西,掩盖着漏洞和特殊的规定,从而使在文字上高度累进的税率在很大的程度上无效。对目前的应纳税的收入施加23.5%的统一税率会得到和施加从20%到90%累进的目前税率同样多的税款。意图减少不均等和促进财富分散的所得税,在实际上却助长了公司收入的再投资,因而有利于大公司的增长,阻碍了资本市场的作用以及使新企业的建立受到妨碍。
意图促进经济活动和物价稳定的货币改革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其后加剧了通货膨胀,因而助长了比以往所经历的更高程度的不稳定。货币改革所形成的货币当局却由于把一个严重的经济收缩转变成为1929—1933年大萧条而对这次灾祸应负主要责任。主要为了防止银行恐慌而设置的制度却在美国历史上造成了最严重的银行恐慌。
意图帮助贫穷农民和消除在农业组织中被断言为非正常状态的农业方案已成为对公款的一种浪费、对资源的一种不恰当的使用、对农民所进行的日益沉重和具体的控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严重的干涉,并且与此同时又对贫穷的农民帮助很少。
意图改善穷人的房屋条件、减少青少年犯罪和帮助清除城市贫民窟的住房方案却使穷人的房屋条件变坏、助长了青少年犯罪并且增加了城市的破败。
三十年代,对整个知识分子而言,“劳动”是“工会”的同义字。相信工会的纯洁和美德达到了和相信家庭和母爱相同的程度。制订范围广泛的立法来袒护工会和促进“公道的”劳资关系。工会在力量上渐渐扩大。到五十年代,“工会”几乎是一个肮脏的名词;它不再与“劳动”具有相同的意义,不再自动地被当作为处于好人的一边。
社会保险措施被制订起来,以便使来自援助的收入成为一个权利,以便消除直接救济和援助的需要。数以百万计的人目前接受社会保险的利益。然而,有待救济的名单却在扩大,而花费在直接支援上的款项上升。
我们能很容易地扩大开列的清单:三十年代的白银购买方案、公用电力方案、战后外援方案、联邦电讯委员会、城市再发展方案、物资贮存方案——这些以及更多的方案具有和原来的意图非常不同而一般与原来的意图极为相反的影响。
也存在着一些例外情况。在全国上下交叉的高速公路、宏伟的横跨大河的堤坝、运行于轨道上的人造卫星都是政府支配巨大资源能力的贡献。尽管具有缺点和问题,尽管存在着很多通过更有效地发挥市场力量来进行改善的可能性,学校制度扩大了美国年青人可以使用的机会,并且对自由的扩展作出了贡献。它是一个证据,表明在各地区学校董事会工作的千百万人的热心公益事业的努力,也表明公众愿意为了他们认为是公共的目标而负担沉重的赋税。尽管具有大量的具体执行的问题,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通过它实际上的存在而促进了竞争。公共保健措施有助于减少传染病。援助措施减轻了痛苦与苦难。地方当局往往提供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条件。法律和秩序得到维持,虽然在许多大城市中,甚至于政府的这种基本的职能尚不能令人满意。作为一个芝加哥的市民,我说这些话是带着个人感情的。
假使把得失加以权衡,那末,我们很难怀疑,其结果是令人担心的。在过去几十年里,政府所从事的较大部分新事业没有达到它们的目标。美国继续在进步:它的公民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并且交通也更好,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区别已经缩小;少数人的集体变为在较少的程度上处于不利地位;一般文化水平飞跃前进。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自由市场进行合作的个人积极性和动力的产品。政府措施却阻碍了而并没有帮助这种发展。我们一直能负担和克服这些措施,原因仅在于市场的极不平凡的生产能力。那只看不见的手对进步的有效作用大于那只看得见的手对退化的作用。 最近几十年,那么多的政府的改革已告失败,光明的希望变成灰烬,这是否为一个偶然事件呢?是否仅仅由于具体方案存在着错误呢?
我相信,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些措施的主要缺陷是,它们企图通过政府来迫使人民为了增进被设想为是普遍的利益而采取违反他们自己直接利益的行动。它们企图解决的是利害冲突的事项、或对利害关系的观点上的差异,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通过建立消除冲突的结构或说服人们改变他们的利益观点,而是迫使人们去做违反他们自己利益的事。他们把局外人的价值判断代替了参与者的价值判断;其办法之一是:由一些人告诉另一些人什么是对他们有好处的;另一个办法是:政府从某些人那里取走一些东西以便使其他人得到好处。因此,这些措施被人们所知的最强大和最富有创造力的一种力量所反对——即:数以百万计的人增进他们自己的利益的企图,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来过他们自己的生活的企图。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措施如此经常的得到与原有意图相反的作用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一个自由社会主要力量之一,并且可以说明为什么政府的规章制度不能制止它。
我所谈的利益不仅是狭隘的关心自己的利益。相反地,它们包括整个一系列人们认为是宝贵的东西,为此他们愿意耗尽他们的钱财和牺牲他们的生命。由于反对阿道夫·希特勒而牺牲生命的德国人是在追求他们所理解的利益。那些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贡献于慈善、教育和宗教活动的男人和女人们也是如此。当然,只有少数人才认为这种利益是主要的。虽然如此,允许这些利益充分发展而不使之从属于统治人类大多数的狭窄的物质利益正是自由社会的优越之处。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比集体主义社会在较少的程度上看重物质。
根据过去的经验,为什么证明这一点的责任仍然似乎落在我们这些反对政府的新方案和企图减少大到已经不相称的政府作用的人的身上呢?让迪赛作出回答:“国家干预的有利影响,特别是立法形式这一方面,是直接的、即刻的和可以说是看得见的,而它的坏的影响是逐步和间接的,并且为人们所不能看到……。大多数人也不会记住,国家检查员可能不胜任、粗枝大叶或甚至偶然贪污化……。很少有人理解到国家的帮助会消除自我帮助这一不能否认的真理。因此,大多数人几乎肯定会出于实际的需要而以过分赞成的态度去看待政府干预。这种天然的偏见只能通过存在于一个社会中的赞成个人自由,即:自由放任的成见或偏见才能加以抵消。因此,对自我帮助的信念下降——这种下降肯定已经发生——的本身足以说明趋向于社会主义的立法增长。”
在今天,自由的保存和扩展正在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一个威胁是明显而清楚的。这是来自保证要埋葬我们的那些克里姆林宫里的坏人的外部威胁。另一个威胁则远为难于辨认。这是来自希望改造我们的那些具有良好意图和愿望的人们的内部威胁。他们不耐烦于缓慢的用说服和例证的方法来完成他们预想的巨大社会变革,从而渴望使用国家权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并且相信他们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假使他们获得了权力,他们不会达到他们直接的目的,此外,他们会造成一个集体主义的国家,在其中,他们会以恐怖的心情退缩下来并会成为其第一批的牺牲者。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意愿而变为无害。
很不幸,这两种威胁相互加强。即使我们避免了一场核屠杀,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威胁要求我们把我们资源相当大的部分用于国防。政府作为我们如此多产品的购买者和作为许多厂商和工业的唯一购买者的重要性已经在政治当局的手中集中达到危险程度的经济力量,改变了私有企业运转的环境和私人经营成功的标准,从而通过这些或别的一些方法来危害自由经营的市场。这种危险是我们不能避免的。但是,通过在与国防无关的领域继续进行目前政府的广泛的干预,并且通过从事没完没了的政府的新方案——从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到月球的探险,我们不必要地使危险加剧。
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在一个国家中可以有大量的破坏”。我们的基本的价值结构和相互交织的各种自由经营的机构可以经受得起很大的破坏。尽管军事方案的巨大数量,尽管在华盛顿已经集中了经济力量,我相信,我们将能保存和扩大自由。但是,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威胁,只有当我们说服我们的同胞们,使他们相信,自由的制度会比强制性的国家力量提供更加肯定的途径、即使有时是较缓慢的途径来达到他们所寻求的目标时,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在知识分子的流行思想中已经明确的变化的闪光是一个有希望的预兆。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财富、贫穷与政治
英文名:Wealth, Poverty and Politic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作者:Thomas Sowell
前言
Thomas Sowell是唯一一位值得我尊重的黑人,他的洞见给了我不少启迪,尤其是“信任半径”这个概念能有效反驳公知及粉红的污蔑之辞,让我对爱有等差的差序格局有了更深认识。中国失落的时间只有四百年不是五千年或是七千年,这是公知、粉红不得不正视的“事实”。。
国家兴衰是自然现象,像中国这种能够屡扑屡起的国家才是极为罕见的。
国家兴衰往往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核心因素是人。。
内容简介
从古至今,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大国崛起、湮灭是常有的事。中国在数个世纪中领先世界各国,后来却落后于工业革命后的欧洲;阿根廷曾领先法国和德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却在半个世纪后陷入政治危机,经济一落千丈。在一国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水平也相差悬殊。美国黑人比白人更容易陷入贫穷,而华人、犹太人和黎巴嫩人不管移民到哪里都能不断创造和积累财富。
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国家的崛起、兴盛和衰亡?又是哪些禀赋让某一部分群体更容易获得财富?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均的成因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大量社会和政治矛盾?
经济学大师托马斯·索维尔在这部全新的作品中,利用丰富的历史材料,通过冷静的观察、精准的分析,深刻地探讨了这一当今世界最具爆炸性的话题。他戳破了权威人士和经济学家模棱两可的数据和耸人听闻的理论,从地理、文化、社会和政治4个方面,以最平实明了的语言揭露了国与国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问题。索维尔的研究超越了不同派系和理论的偏见,不仅为我们揭露世界的真相,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思考和认识世界本质的方法。
名人推荐
本书极具价值,揭露了政客和知识分子在贫富问题上的无知以及他们的主张的煽动性。索维尔博士纠正了政客、知识分子和各种骗子关于收入的说法,而且读起来非常有趣。
——沃尔特·E. 威廉姆斯(Walter E. Williams)教授,乔治梅森大学
在索维尔的这本最新著作中,凝聚了他长期研究的成果,他质疑了美国公共政策的基本假设,并紧紧围绕他一直强调的——基于事实。
——杰森·莱利(Jason Riley),《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托马斯·索维尔理应拿诺贝尔奖。没有人像他一样写了这么多有洞见有深度的著作。他的最新作品是又一次令人震惊的观察,揭露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无知。他给我们呈现了文化、地理、政治和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社会进步(或退步),这让沉迷于政治正确的人感到愤怒,却会让其他所有人更加明智。
——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福布斯杂志》(Forbes Magazine)
索维尔把我们当前的争议放在国际背景下,这真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我数下来,索维尔写了52本书,包括1971年写成的《经济学:分析与问题》,其中的精准分析和无畏的评论一直为读者倚重……他的著作清晰明了,没有学术术语,也没有炫耀专业知识(很多学术写作就毁在这一点)……他的大部分著作仍在重印,这是对读者所付出的时间的回报,本书也是一样。
——《美国观察家》(American Spectator)
本书应该是2016年美国大选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索维尔博士的这本书是科学与常识的巧妙融合,它揭示了为什么有些群体会陷入贫穷,以及社会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使他们摆脱贫穷……每个总统候选人都应该读一读本书,所有竞选代理人应该好好理解这本书……《财富、贫穷与政治》一书为消除争议提供了必要的敏锐知识武器,它提供的智慧可以帮助保守派设计出真正有所作为的政策。
——《布莱巴特》(Breitbart)
本书对经济成功和失败的普遍原因的解释极具争议性……尽管索维尔没有给出任何轻易的解决方案,但他隐含的论点是,表现不佳的国家要认真地改变经济前景,文化因素必须发生改变。这一点值得深思。
——《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作者简介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美国当代杰出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现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在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等讲授经济学,还在政府部门担任经济学顾问,获得过包括总统人文成就奖、全国人文学科奖、布莱德雷基金奖在内的众多荣誉。
他的著作有《美国种族简史》《知识分子与社会》《实用经济学》《被掩盖的经济真相》《房地产的繁荣与萧条》《知识和决策》等30多部作品,其中一些甚至多次再版。他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Basic Economics)一书已被译成六种语言。其文章和随笔多次发表于《财富》《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知名媒体。
目录
第1章 重大问题
今天的人们也许震惊于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在生活水平上的极端差距,但纵观有记载以来的人类历史,地区间的财富差距是一种常态,而且这种差距还扩展到了创造财富的因素,包括知识、技能、习俗和行为举止等。不同地区不仅地理、文化和政治背景差异较大,而且在这些因素的发展上也不平衡。
数千年来,财富以及创造财富的能力在不同地区的巨大差距久已有之。虽然这种经济不平等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但近几个世纪以来,不平等的模式发生了巨变。曾经的古希腊远比英国发达,但英国在西元19世纪引领整个世界进入了工业时代,它远远领先于当时的希腊。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发达。中国拥有包括指南针、印刷术、造纸、船舵和瓷器在内的众多创新与发明,而且中国掌握铸铁技术也比欧洲早一千年。西元15世纪,东西方各有一位航海家进行了“发现之旅”,相对于哥伦布航海,郑和下西洋开始的时间更早,航期更长,船队也更大更先进。但几个世纪之后,中国与欧洲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反转。不论今天的世界财富格局如何,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曾在某些领域领先或拥有过众多专长。
欧洲的农业是由中东传入的。在人类社会的演化中,有很多改变人类生存方式的进步,农业或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在狩猎——采集式生存方式下,人类为了食物必须得游牧大片土地,而农业的传入使得人类可以永久定居于人口密集的社区,修建城市由此变得可能。不仅如此,相比散居于偏僻地区的生存方式,同样数量的人口聚集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创造的艺术、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其人口规模。
希腊比北欧和西欧更靠近中东地区,农业更早传播到该地区,因此希腊的城市化进程也比欧洲其他地区提前数个世纪。它很早就享受到城市人口聚集带来的各种好处,因而在许多方面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随机的某个地理区位不会造就天才,但能为人们提供开发自身智力潜能的环境。疲于四处游猎、搜寻食物的狩猎——采集式生存方式是不可能开发自身潜能的。
地理只是造成人群和地区间经济差异的众多因素之一。尽管生活水平的差异也很重要,但经济差异并不限于此。地理位置不同,人们所处的文化世界也不同,或广阔,或狭窄,扩大或限制着人们自身智力潜能的发展,经济学家将这种智力潜能称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地理位置的差异不仅有水平上的差异,比如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不同;也有垂直上的差异,比如平原和高山。有一项地理研究发现:
山区不利于天才的发育成长,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分散又相互隔绝,远离人与观念大汇流的河谷地区。
不论是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脉、摩洛哥的里夫山脉,还是希腊的品都斯山脉、亚洲的喜马拉雅山脉,世界各地的山区都表现出相似的贫穷与落后的模式。法国著名的历史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指出:“山区会持续落后于平原。”过去数千年里一直如此,直到近两个世纪交通与通信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外界的进步才越来越多地进入与世隔绝的山区村庄,虽然这些进步已稍显滞后。然而,人们在更适宜的环境中创造的文明是无法通过技术变革完美复制到山区的。生活在山区的人当然可以努力追赶,可是其他地区的人不会停滞在原地。
山脉仅是地理特征之一,地理又仅是影响人类发展的因素之一。不论是地理形成的物理空间隔离还是文化隔绝,它们曾反复出现,造成了世界各地的贫穷与落后。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考察造成隔离的原因。
不论原因何在,当今世界如同古代一样,不同群体、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非常普遍。……
不仅国家间存在收入差距,一国内部不同阶层、种族和细分人群之间的差距同样显著。各国的应对方法五花八门,从政客辞职到革命。许多人相信他们国家的经济差距即便不是危险的,至少也显得很奇怪。鉴于此,有必要指出,这类差距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存在于历史的各个时期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因此对经济差异的解释也不应限定为特定时间或地点的特别因素,例如现代资本主义或工业革命,更不应是那些政治上合意的或能满足情感诉求的因素。
不应想当然认定,那些能引起重大道德争论的因素如占领、奴役,是当代经济不平等的决定性根源。它们在某些情形下可能是决定性的,也可能不是。国民或国家的富裕与贫穷,可能是因为(1)他们比别国生产得更多或更少,(2)他们夺取了他国生产的财富,(3)他们生产的财富被他国夺去。不论你更愿意接受哪种解释,事实都不会改变。
举个例子,西班牙征服西半球国家,不仅残暴地对待当地土著,毁灭了美洲古代文明,而且通过洗劫当地土著,强迫他们在金银矿劳役,将西半球的财富——200吨黄金和超过18000吨的白银11——运到西班牙。有过这一行径的,并非只有西班牙。但问题是,财富转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今天世界各国的经济差异?
西班牙在今天不过是西欧相对较穷的一个国家,在经济总量上被瑞士、挪威这些从未成为过帝国的国家所超越。在“黄金世纪”涌入西班牙的财富本可用于投资经济或人力资本,但大部分财富被消费掉了,没有用于投资。用西班牙人自己的话说,“金子像洒落在屋顶上的雨一般涌入西班牙,但立刻就流走了”。在人类历史上,这非常常见。不论是征服还是奴役他人,结果无他,不过是精英统治集团一时的发财致富。
道德上看,西班牙殖民者在西半球国家造成了永久性破坏,但带给西班牙经济长期繁荣的因果效应非常小。晚至1900年,超过一半的西班牙人还是文盲,同期的非洲裔美国人被解放还不到50年,大部分已经能读会写了。而100年后的2000年,西班牙的人均收入甚至略低于非洲裔美国人。
【注:投资而不是消费确实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小岛经济学》也是这种看法。】
道德问题与因果问题都很重要。但将两者混淆,或假想将两者打包成一个政治或意识形态上吸引人的答案来解释经济差异,绝非有效的研究方法。
国与国的经济差距只是经济不平等的一部分,一国内部的巨大经济差距同样值得注意。在讨论一国内部不同人群的经济差异时,人们倾向于将这些差异当作“收入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问题。但真实收入(经通胀水平调整后的货币收入)是指一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仅从生产商品和服务而获得收入的生产者的视角考察这一产出,很可能会产生不必要的谬误,而这些谬误又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国的生活水平更多地取决于该国的人均产出,而非生产获得的货币收入。否则,政府只要印更多的钞票,就能让大家都富裕起来。聚焦于“收入分配”问题,让人觉得政府似乎能重新调整货币流,让收入更公平——不论公平如何界定。人们没有考虑政府的政策可能对生产过程造成的根本性影响,而一国的生活水平正取决于生产过程。媒体甚至学术界常常有这样的观点:产出或财富似乎无缘无故就出现了,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分配。
【注:例如罗尔斯这厮写的《正义论》不提生产,全程讲分配,讲“阶级斗争”。。】
有时,过度关注收入分配,会使人忽视背后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并因此将富人的收入解释为“贪婪”——就好像对金钱永不停止的欲望就会让别人为买东西付出巨额金钱。
造成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收入与财富差距的潜在因素众多,其中有一个因素最明显却常常被忽略。正如经济学家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指出的:
贫穷真正的问题不是分配,而是生产。穷人之所以穷,不是因为某些收入被夺走了,而是因为他们无法生产足够的产出使他们能摆脱贫穷,不论原因为何。
亨利·黑兹利特如此明了的事情,对于其他人却并非如此。他们看到的是不同的视野,由此也会提出另一项议程,认为经济差异是源于财富从某些人转移到了另一些人。
历史表明,造成经济差异的原因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中。我们将从财富生产的差异来解释经济差异,当然也会提到财富转移,它过去通过征服或奴役实现,如今则通过福利制度进行内部财富转移或国外援助实现。
当我们考察地理、文化和其他因素对财富生产的影响时,我们应区分“影响”(influence)与“决定论”(determinism)。曾经有人将他们对经济差异的解释建立在“地理决定论”(geographic determinism)上。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被认为更富饶。批评者很容易指出,这并不一定总能成立,甚至在大多数情形下都难以成立,因为既有类似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这样资源丰富但非常贫穷的国家,也有日本和瑞士等自然资源匮乏却富裕的国家。这一事实使得一些人不仅否定地理决定论,而且否定地理是一个主要影响因素。
但是,地理因素会通过其他不同的方式影响经济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些影响不一定是由于特定地理特征带来的隔离,更多的时候是特定地理特征与其他地理特征的相互作用,以及地理特征与非地理特征如文化、人口、政治及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
同样,特定地理因素与其他非地理因素相互影响带来的结果,也不同于特定地理、文化、人口或政治因素各自带来的影响。这就是“影响”不等同于“决定论”的原因所在。虽不是大多数,但许多经济结果取决于不止一种因素,在各种不同因素共同作用下,全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具有相同的繁荣与进步程度的概率几乎为零。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只是造成经济结果不平等的众多因素之一。
另一个因素是文化,不同人群、不同国家的文化具有巨大的差异,甚至一国内部不同群体之间也存在差异。类似于对地理影响的批评,对文化影响的批评有时同样借助于一个过分简化的想象。《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就曾试图否认文化因素对经济结果产生影响。它拒绝承认从英格兰继承的文化才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曾经是英格兰殖民地的国家经济发达的主要原因:
加拿大和美国曾经是英国殖民地,但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曾经也是。这些前英国殖民地如今的贫富差异巨大。因此,英国遗产并非北美国家成功的原因。
尽管这些国家都曾是英国殖民地,可以认为受到英格兰文化的影响,但建立加拿大和美国的是浸润了英格兰文化的英国人的后裔,文化的影响在以后的数个世纪逐步展示出来。而生活在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的人,所处的是数千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英格兰文化带来的冲击影响还不到一百年,在他们成为大英帝国一部分的短暂历史中,他们自身的本土文化仍然在产生影响。
【注: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香港的崛起和大陆、北韩、越南的落后形成了鲜明对比。】
也有许多前英国殖民地的居民为非英语民族,它们在独立以后仍能看到英国文化的烙印,例如律师在法庭戴假发。但外在的英国传统仪式不会阻止这些前殖民地在独立之后拥有根本上不同于英国的文化遗产,以及非常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历程。
“基因决定论”(genetic determinism)者同样不相信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先天的智力差异能够解释种族、国家与文明间的经济不平等。基因决定论基于无可辩驳的当代人在各种成就和智力测试成绩上的差异,但该理论无法解释特定种族、国家或文明在特定历史阶段曾经远远领先,又在其他时期远远落后,比如英国与希腊的角色反转。
一些国家曾在一个世纪之内从落后贫穷的国家攀升到人类成就的前列,如西元18世纪开始追赶的苏格兰和19世纪开始追赶的日本。这种变化远远快于基因构造的变化。事实上,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发现基因变化的迹象,但是他们在文化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定文化的源泉会在时间的迷雾中消逝,这一点也许令研究者沮丧,但文化在当今的表现仍清晰可见。一位当代基因决定论者曾指出,文化无法量化或统计,无法用来分析IQ与GDP之间的相关关系,也不能满足科学精确度量的要求。但统计学家经常指出,相关关系不是因果关系,正如凯恩斯很早告诉我们的:“大致正确胜于精确的错误。”
不论我们考察的是文化、地理、政治还是其他因素,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我们理解“影响”不同于所谓的“决定论”的重要原因。
第2章 地理因素
世界从来不是公平的竞技场,一切皆有成本。——戴维·S.兰德斯(David S. Landes)
这些自然现象展示了地理条件不同造成的各异的物理效应。此外,地理现象同样也会造成各异的经济与社会效应。人们踩在脚下的土地是不同的。科学家称之为软土的肥沃土壤在全球的分布既不是均匀的,更不是随机的,而是集中在南北半球的温带地区,热带几乎没有。
几千年来,农业一直是人类最普遍且最重要的经济活动,直到近几个世纪,个别幸运地区才出现例外。在这数千年中,土壤分布尤其重要。在迥异的地理环境中,经济与文化的演化面临的经济约束也不同。
地理差异对经济的作用,会直接影响生活水平,也会间接影响人的发展。这取决于特定的地理环境究竟是促进还是妨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任何社会都无法独占推动人类发展的发现与发明,所以不论哪一个阶层、种族和国家,能够接触到世界其他地区将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拥有更大的文化视野很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更大的文化视野有利于传播产品、技术和知识,更重要的是,当人们一次次地看到其他地方的人用另一种方式去做事时,他们会打破人类用习惯方式做同样事情的惯性。在许多与世隔绝的社会中,人们做事的方式世代相传一成不变。据说,“有智慧的人才会在挑选食物时比较它们的营养价值”。
隔离会带来相反的影响。当西班牙在西元15世纪发现加那利群岛时,他们发现岛上的人还处于石器时代。西元18世纪英国人发现澳大利亚土著时,情况与此类似。在其他相似的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也是如此,不论是遥远的山村,还是热带丛林深处,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几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的其他地区的人一样。
另一个造成人们与世隔绝的地理因素是沙漠。……
尽管地理影响重大,但地理决定论并不可靠。因为人们会与其他地方的人接触,即使地理环境没有发生变化,人们也会与不断变化的人类知识以及具有迥异的价值和抱负的不同人类文化相互作用,因而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情况也完全不同。自然资源对今天的我们是有用的,但它们中的大部分对史前石器时代的穴居人并非如此,因为他们不掌握如何让这些资源为我所用的知识。自远古以来,中东地区就有丰富的石油储量,但直至科技发展,世界其他地区建立了工业国家,中东的石油才成为贵重的资产,同时深刻地改变了中东地区及其他工业国的生活。
个别的地理影响因素不能孤立地考虑,因为它们的相互作用对于结果至关重要。降水量与土壤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同地区的降水量不同,而且土壤对于降雨的涵水能力也有很大的差异。巴尔干半岛石灰土的涵水能力就比中国北方的黄土差。气候与土壤会影响各地粮食的生长情况,而农业是过去一千年中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也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因此各地几乎不可能实现同样的繁荣程度。
与其他事情一样,土壤涵水能力仅在一定范围内是有益的。回到罗马世纪,在欧洲西北部大平原,雨量丰沛,沼泽遍布,成为发展农业的障碍。经过几个世纪的排灌技术发展与应用,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土地才变得肥沃可耕种。土壤肥沃程度既非天生的,也非固定不可改变的。灌溉与排灌技术的发展,用马或牛来翻犁黏土,这些都极大地改善了土壤的肥沃程度。土壤、降雨以及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与技术,这三者相互影响,使欧洲西北部土地变得越来越肥沃。
【注:这段可以和伪史论的论证结合起来。】
这意味着地理因素的排列组合远远超越了单个因素,特别是与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一起考虑。因此,比起单个地理因素造成的差异,不同的地理环境相互作用会带来众多的经济与其他结果,而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差异将更大。全世界各地的部落、种族与民族拥有不同的地理环境,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传统,因而不可能具有相同的生产力水平。
不仅不存在相同的经济结果,而且一个时代的不平等模式与另一个时代也极其不同。
古希腊相对于古代英国的巨大优势,反映出希腊具有更毗邻中东的地理优势。当时农业在中东发展起来,先扩散到邻近的东南欧地区,数个世纪后才扩散到整个欧洲和其他地区。没有农业,几乎不可能或很难形成人口密集的城市社会。居无定所的游牧者要在大片土地上游猎,以此获得足够的食物来养活一定数量的人口。
【注:中东地区能更早发展农业、更早进入文明社会,极有可能是更靠近中国的缘故。】
直到今天,城市依然是大部分文明进步的源泉。由城市人口创造的文明进步,特别是里程碑式的科技成就,远多于其他环境。居住在那些不利于城市形成的地理环境中的人,长期落后于身处有利于城市化的地理环境中的人。在人类史上,城市发展与我们称之为文明进步的大多数事物一样,出现得相对较晚。农业不仅使城市成为可能,而且使工业、医学以及其他在城市环境中取得的进步成为可能。
现代交通与通信的进步能够突破隔离,正如其他技术进步能减轻甚至消除某些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构成障碍的地理因素。但地理隔绝严重的地区经历了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差异,新近的科技进步无法回过头来消除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相比之下,有些地方的居民数千年来已经习惯于接受世界上其他人群的成就与观念。
我们如何定义“环境”至关重要。一位知名地理学者的定义是,“环境是人们所居住的物质环境”。但另一位地理学家说,“环境不仅仅是所处的地理条件”,他呼吁提出“一个涵盖范围更大的环境定义”,指出过去祖先的经历会“以天资和从遥远祖宗那里继承的传统习俗在当代族群身上留下痕迹”。不论从地理角度还是从社会经济角度描述环境,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将环境定义为特定群体周围的东西,还是同时包括群体内部的东西。
过去的环境条件塑造了当今人们所处的物质与精神世界,不了解这些环境条件,我们就很难理解今天发生的一切。因为无论好坏,今天都是过去的遗产。正如一位文化史学者指出的:“人不是空白的碑,不可能擦去环境镌刻在其身上的文化来为雕刻新的文化腾出空间。”另一位知名历史学家指出:“不是我们生活在过去,而是过去存在于我们中间。”
在此背景下,我们将详细考察水路、山脉、动植物等地理因素的影响。除了这些特定的地理特征,地理区位自身也是值得强调的一个因素。
水 路
水路有多重作用,包括为人和动物提供饮用水,为鱼等提供食物,是灌溉农作物的源泉,并且是运输人和货物的大动脉。在扮演的所有角色中,不同水路有差异,对人类的价值也不同。
水路最不可或缺的功能是为人和动物提供生存所必需的饮用水,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作为交通运输的动脉这一功能上。作为运输大动脉,水路运输与陆路运输在成本上差异巨大,特别是在两百年前,汽车运输方式还没有出现的中世纪,这种差异更大。
例如,西元1830年的时候,通过陆路将1吨货物运送300英里成本是30美元,而通过水运跨越大西洋运送3000英里的成本仅为10美元。由于运输成本的差异,高加索山脉第比利斯城虽然离巴库油田的距离仅341英里,它却通过水路从8000英里外的美洲进口石油。类似地,19世纪中期美国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以前,相比于从密苏里河岸走陆路,货物从中国港口横跨太平洋可以更快更便宜地送达旧金山。
鉴于食物、能源及其他必需品要从城外运到城市,同时大量的城市产品要运出去销售,全世界那么多城市位于通航水路上也就不奇怪了。尤其是以发动机为动力的陆路运输方式还未出现以前,情况更是如此。
从另一个方面看,没有适航水路的地方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将会大大受限,也会缩小接触的文化范围并减少与其他远距离群体和文化交流的机会。在某些情形下,缺乏水路或存在其他地理障碍意味着相距很近的群体可能也很少联系。在现代运输与通讯方式出现以前的数百年里,在那些缺少马、骆驼或其他驮兽的地方,情况更是如此。
非洲大陆的一个特征是,尽管面积超过欧洲的两倍,但海岸线却比欧洲短。欧洲的海岸线更曲折,形成了许多港口,便于轮船停靠躲避波涛汹涌的海浪。此外,欧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面积由众多岛屿和半岛组成,这也大大增加了欧洲海岸线的长度。
相反,非洲海岸线更平直,很少凹陷,意味着缺乏优良的天然海港。另外,岛屿与半岛仅占非洲陆地面积的2%,数量比欧洲少得多。与此同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的沿海水域很多是浅滩,难以供远洋航船停靠。在这些地方,大型远洋航船必须离岸抛锚,将货物卸到能在浅滩航行的小舰船上,再运上岸。这一过程极其费时费力,而且成本高昂,往往不可行。几个世纪以来,欧亚之间的海上贸易船舶途经非洲,却几乎很少停靠。
即使在少数地方大型船只能够通过深水河流进入非洲,沿海狭窄的平原也会突然被海边断崖阻断。这种地形带来的结果是,即便船只能顺流而上进入非洲,也会碰上瀑布而无法进一步深入大陆。基于同样的原因,从非洲内陆顺流而下的船只,也无法像在欧亚大陆或密西西比河的部分河段一样驶入大海。
与非洲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有一个堪称“世界独一无二”的密集水路网络可以通航,由长江及其支流和遍布港口的锯齿状海岸线组成。同样独一无二的是,在欧洲处于中世纪时,中国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中国的水路在港口和河流类型上都不同于非洲。非洲是一个干旱的大陆,许多河流不够深,无法像中国、西欧或美国那样使装载大批货物的大型船舶通航。即使在罗马帝国时代,最大的船也无法在尼罗河上航行,更不必说今天大得多的船了。
即使在同一大陆内部,西欧的河流也不同于东欧或南欧,更不必说完全不同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了。宽广的海岸平原,海拔不超过1000英尺,意味着西欧河流流淌得很平缓。在动力船能够在汹涌的河流中航行之前,这一特征尤显珍贵。那时许多地方的原木能够顺流而下运到下游,但负责运送的人只能走陆路返回。
西欧的河流通常汇入大海,由此可以接入全世界各地的海港。东欧和南欧的河流则非常不同,于是也就影响了流经地人们的经济和文化。越往东,墨西哥湾洋流带给欧洲气候的增温效应越弱,东欧河流在冬季冰封的频率更高,封冻期也更长。
东欧河流即使未冰封,它们也通常是汇入湖泊或内海而非流入公海。例如,多瑙河、顿河、第聂伯河流入黑海,伏尔加河流入里海。俄罗斯的河流大部分汇入北冰洋,但北冰洋不像大西洋或太平洋,它很难与世界其他地方相通。数个世纪以来,东欧在经济上落后于西欧的原因众多,水路差异是其中之一。
南欧河流对这一地区经济的贡献更小,部分原因是当地的主要河流相比西欧或东欧要少,另一部分原因是在地中海地区冬季暴雨,夏季少雨,河流几乎干涸。而巴尔干山脉的河流又太过峻急,除了当地的小船,不适宜其他船只通航。
【注:古希腊、古罗马是如何依靠古埃及的粮食过活的???】
相对于其他西半球国家,美国在水路上拥有巨大的地理优势。用著名经济史学者大卫·S.兰德斯的话说,美国“有曲折的海岸线,其间遍布优良海港”。美国还拥有许多大江大河,其中最壮观的是密西西比河。不像非洲河流急速流下——扎伊尔河在150英里的距离内有超过30个大瀑布,落差接近1000英尺,密西西比河的河床每英里仅下降4英寸。尽管尼罗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但密西西比河注入墨西哥湾的水量是尼罗河注入地中海的数倍。河流的价值就在于水量多少,密西西比河径流量远多于尼罗河,尽管后者流经距离更长。
尼罗河承载大型船只的能力很有限,美国的哈德逊河以及旧金山港和圣迭戈港却都是深水良港,可供航空母舰停靠。五大湖是一个大型的相互连接的水路系统,其中密歇根湖的面积比以色列还要大,而苏必利尔湖又比密歇根湖还要大。这些湖都足够深,能让远洋船通航其上。自西元1959年对圣劳伦斯河进行人工改造后,远洋船可从大西洋一路上行,直抵芝加哥和五大湖地区的其他中西部城市。
水路不仅在不同的地方各有不同,它对人类的重要性在各个历史时期也会发生变化。以地中海为例,数个世纪以来,它是比大西洋更有吸引力的水路。直到知识和技术进步,两者的地位才有了改变。在此之前,地中海非常适合航行:
漫长的夏季,晴空万里,夜晚星光闪烁,风向稳定且无雾。这对航海是绝佳的季节。习习的微风有利于外出或归家的航船,无数的海角和岛屿清晰可见,布有航标以便航船绕开,这在指南针发明以前非常重要。
在人类学会在缺乏路标指引且目力所及全是水的环境中航行之后,海洋才从运输的障碍变成通途。只有科学、数学和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克服这一根本性障碍,大洋航行才有可能实现。最开始人们是观察白天太阳的位置和夜晚星星的位置,通过这些天空中的路标来判断航海的方向,磁罗盘的发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更便捷,即使乌云遮蔽天空也不受影响。
地中海温和浪平,而大西洋风急浪狂,因此长期以来,地中海沿岸港口的贸易活动都要比西欧的大西洋海港更繁忙。欧洲人发现西半球之后,欧洲国际贸易的主导方向也发生了改变。大西洋航行环境更恶劣,需要的船只类型也不尽相同。相对于大西洋,地中海的商业统治力和制海权变得黯然失色,而且西欧大西洋海港的船只更能适应新的跨洋贸易的需要。大海还是大海,知识与技术进步改变了其经济和其他方面的重要性。
尽管渔村无法达到由农业供养的城市那样的人口聚集水平,但也代表了从狩猎—采集社会到定居生活的跃进。不过,供应本地区以外市场的商业性捕鱼活动,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在地中海地区,土地的农业产出极少,当地人为了谋生,要同时利用陆地与海洋的产物,这与其他地方将农牧业相结合类似。
水路与水路各不相同,同一类型的水路也各有差异,它们对人类而言具有各不相同的有用特征,这些特征的排列组合极其多。因此,对世界各地的人而言,水路带来的价值不可能完全相同。更不必说水路在一些地区分布多一些,在另一些地区很少,而沙漠中根本没有水路。
陆地与气候
陆地有许多面貌。简单来说,陆地的形状决定了水的流动,并由此影响生活在特定区域的人类的命运。土壤的物理特征和化学成分就像气候一样,对农业至关重要。陆地的类型如山脉、沙漠、大裂谷将人群分隔开来。巴尔干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们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山地群体,就是这样被隔绝于世的。
山脉
山脉会同时影响居住在山上和山下的人们的生活,但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是迥异的。
全世界大约10%~12%的人口生活在山区(其中大约一半在亚洲),大约90%的人口生活在海拔不超过2500米的山区。山区人口密度往往相对较低。生活在山区的人形成了特定的生活模式,不论他们是在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脉、摩洛哥的里夫山脉、希腊的品都斯山脉,还是在亚洲的喜马拉雅山脉。最常见的是贫穷、隔离与落后。不难发现造成这种模式的原因。山地的自然特征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无法获得在其他地区带来繁荣与联系的许多进步。
不只是基础设施和技术发展,平原上的流行文化也滞后了许久才传播到山区。尽管数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教一直是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主导宗教和文化,但亚美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相邻山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却是完全不同的。摩洛哥的里夫山下的人成为穆斯林的几百年后,里夫山区的人才最终接受了伊斯兰教。
同样,语言也是慢慢从低地传播到高地地区。苏格兰低地人讲英语很久以后,盖尔语还在高地地区流行了很久。希腊品都斯山下的人说了上百年的希腊语,山上的人还在说罗马尼亚语。语言差异会增加山区之间的隔离,特别是当外界听不懂山里人说的本地语言或方言时更是如此。新几内亚有超过1000种语言,其中70%以上都来自仅占该岛三分之一面积的山地地区。在世界各地,与世隔绝的山区普遍都拥有多种语言和方言。
山区也更难构建与维持法律和规则这类社会性基础设施。即使名义上山地在一国或君主控制下,但这种控制时断时续,也并非一直有效。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黑山地区、摩洛哥苏丹治下的里夫山脉和莫卧儿统治下的印度高地地区。苏格兰的高地地区和殖民地时期的斯里兰卡高地地区,在其邻近的低地地区被占领并纳入另一种文化环境后,依然长久保持独立。在过去许多世纪中,全世界各地山区的人抢劫和掠夺更富有的低地地区的人,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山区的贫穷,并不仅见于这个意大利小山村。20世纪的一个牛津大学学者这样谈到希腊:“我曾见过一个在乡村长大的希腊人,12岁以前他连橄榄树、鱼,甚至橘子都没见过。”
在环地中海国家的诸多山村中,农民偶尔才能吃上肉,只有少数幸运的村庄才有奶酪,这是很常见的状态。农民的一日三餐都是面包;若往前追溯,妇女为家庭缝制衣服;到了冷天要将牲畜引入室内,人畜共处一室。一本记录西方文明史的里程碑式著作提到:“只有最富有的人才有足够的木头,可以将人的住所与牲畜棚分隔开来。”一位旅行者在西元1574年经过保加利亚山地时说,他自己宁可在户外大树下露宿,也不愿睡在山区农民的小屋里,“因为小屋人畜共住,环境污浊,散发恶臭,让人难以忍受”。
这种一般化的结论当然并不适用于每一个山区村庄。但总体来看,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山区和高地大多都具有这样的模式。西元20世纪对喜马拉雅山区一个村庄的研究发现,20%的新生儿不到一岁就夭折了。即使是繁荣的美洲大陆,西元20世纪初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农民样本群体显示,在沿海平原的农民挣得的收入是山区农民的3~5倍。
即使到了西元20世纪初,大多数山里人从事的仍是自给自足的温饱型农业。伴随着山区生活的负面经济后果而来的,是人力资源发展的负面后果。在全世界的许多山区,人们挣扎求生,儿童很小就辍学去工作。这样一来,他们与山外更广阔世界中的知识也隔绝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文盲在环地中海山区很普遍。
很少有人会从山下搬到山里生活,过去尤其如此。而山里人到低海拔地区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们很难适应山下的世界,他们往往因季节性工作而短暂逗留,并且经常被排斥。这种情况持续了几百年。……
20世纪美国对山民同样采取抵制态度。看看大批山区人涌入城市社区时媒体的反应就知道了。一项关于山区移民的学术研究描述了《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反应,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山区乡巴佬被刻画成一群堕落的人,他们“生活水平和道德水准都很低……大多数时候是手段残暴的醉鬼”。全国性的报刊如《时代周刊》(Time)、《展望》(Look)、《哈珀斯》(Harper’s)随后也进行了报道,题目如“山里人侵入芝加哥”。这篇文章的小标题表达了种族隔离的意思:“这座城市的族群融合最困难的不是与黑人的融合……这个城市中有一小部分白人新教徒,还有一些从南部移民而来的早期美国移民,这些人通常自负、贫穷、原始,而且很容易动刀子。”……
山里人同黑人的对比超越了其他人的想象。一项1932年的研究调查了蓝岭山脉小社区中的白人儿童,结果显示这些儿童的IQ某种程度上甚至低于全美黑人儿童的平均水平,当时黑人儿童的平均分为85分,全国平均为100分。而且山区儿童在IQ模式上也与黑人儿童非常相似,他们都不擅长抽象问题,最初几年他们也许与全国平均成绩相近,但越长大,差距越大。
另一些关于山区儿童的研究发生在1930年,调查对象是东田纳西地区的学校,这项研究发现了相似的趋势。这些儿童两次IQ测试的中位数分别是82分和78分。在得分更高的那次测试中,6岁儿童的IQ测试中位数是95分,16岁青少年的IQ测试中位数下降为74分。10年后,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教育水平提高,东田纳西社区的这些学校中的儿童IQ成绩中位数提高到了87.6分。
尽管山地会给生活在山上的人带来负面影响,但对于山下的人是一种福利。当携带丰沛水汽的风遇到山坡而爬升,与更冷的空气相遇会带来雨和雪。通常山地迎风面的降雨量是背风面(即所谓“雨影区”)的数倍。随着雨水顺山坡流下,形成涓涓细流,进而又汇成溪流,无数溪流最终汇聚成河流。这对于山下的人们有许多用处。全世界主要河流均发源于山区。
有些山区的降水多为降雪,水不会一下子释放出来,而是在温暖的季节里融化成水慢慢流出。这意味着,河流流动并非完全依赖于即时的雨水,旱季时山上的融雪为河流补充了水量。
土壤与气候
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中,没有什么发明比农业带给人类的影响更大。人类经历了漫长的进化,才学会种植想要的食物,在此之前要么采集大自然馈赠的食物,要么捕鱼或养殖驯化的动物。事实上我们视为文明的所有事物,包括城市,都起源于农业。
农业本身是如何兴起的,这一问题的答案已经消失在古代的迷雾中。但是,我们知道农业是如何来到西方世界的。它在数千年前从中东地区传播过来,起源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即今天的伊拉克。在当时的知识水平下,那里的地理环境很适合农业兴起。
最早的农民也不是无师自通就知道庄稼生长会消耗土壤中的营养成分,他们也不知道要让土壤源源不断地产出需要为土壤补充营养素。实际上居住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地区的农民不必知道——每年泛滥的洪水冲刷会给土壤带来新的营养成分,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尼罗河流域,造就了古埃及文明。
由此我们也再一次看到,地理的差异给人们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命运。而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平等延续到了今天。就像我们已指出的,最肥沃的土地在全世界的分布既不是均匀的,也不是随机的。绝大部分极肥沃的土地分布在广大的欧亚大陆,始于东欧,延伸到中国东北。
热带非洲每亩土地的产出远远低于中国或美国。表层土较浅使得植物根部没有空间延伸触及地下深处的营养素和水分,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土地的缺陷之一。更重要的是,由于非洲土壤干燥,阻碍了人们利用肥料补充土地缺少的营养素。当土地缺乏足够的水,使用化肥不仅不会促进庄稼生长,反倒会妨碍生长。
泛泛而谈时,我们可以讲热带气候、温带气候或北极气候,但特定问题中说到特定地方如城市的气候时,就必须考虑该地区特定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更一般地说,要理解经济和社会结果,我们必须考虑地理、文化、政治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及相互作用。
温带地区的国家通常比热带国家在经济上更发达。热带有消耗人精力的高温或流行疾病,而在温带地区,寒冷的冬天杀死了致病的微生物。许多研究者以此来解释温带比热带发达。我们也已知道,最肥沃的土壤很少出现在热带地区。但是,许多人从热带之外的地区到热带定居并且发财致富,并且外来人通常比当地人更容易成功。东南亚的华人群体和西非的黎巴嫩人就是典型例子。
【注:黎巴嫩在西亚,不是西非。】
在澳大利亚定居的英国人更令人吃惊,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占多数人口的人群,而澳大利亚国土面积大约有40%属于热带。处于热带的夏威夷绝大多数人口的祖先是日本人、中国人或欧洲人,他们在今天依旧很成功。
通常而言,人们总是觉得,相比于来自其他环境的外来人,当地人最能把握当地地理环境的机会,也更有能力应对地理环境的不利影响。但证据显示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地理环境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直接带来的经济益处或发展障碍上,它还会产生间接影响,促进或限制人力资本(包括知识、技能、习惯或价值观)的发展。
倘若温带的地理环境形成的人力资本能在任何气候环境中获得成功,从温带移居到热带的人比当地人更容易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如一位著名地理学家的观察,特定的文化“在那些永远无法涌现这些文化的地区”也能扎根。
温带的文化为什么在其他无法产生这些文化的地区中具有同样的价值呢?
温带与热带最大的社会差异并非平均温度相差悬殊。在中世纪,温带地区的人面临的生存威胁,是在时间短暂的春夏季节种植足够的粮食作物,以便熬过全年,包括寒冬腊月。为了生存,人们无法逃避,必须在春天土地解冻后耕犁或敲开土地,以便及时耕作。
【注:欧洲中世纪懂得耕犁???】
这就意味着生活在四季更替地区的人们有一种时间紧迫感,并形成了根据需要随时调整的纪律意识。在全年能够耕种、收获食物的地区,这种品质就不那么有必要了。更不必说,大自然为许多热带地区提供了非常多的食物。
生活在温带,人们还必须为冬天储藏食物。这不仅意味着形成储存以备不时之需的危机意识,而且要求将易变质的食物如牛奶和水果加工成可储藏的奶酪和果酱。这在热带也不是特别有必要,而且热带食物如香蕉和菠萝在炎热气候下比寒冷气候下的小麦或土豆更难储藏。
现代经济和技术条件使我们不必再操心这些事,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视这些事情对于古代人的生存是如此重要,因为那时候人们还无法长距离大批量运输食品,也没有冰箱和冷库。
动 物
地理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经济和社会结果。当欧洲人到达西半球时,整个西半球没有马、牛或其他能驮重物的役畜。
在机动车发明之前的中世纪西欧,从运输到耕地再到战争,所有这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牛马。没有牛马,整个西欧经济社会演化会完全不一样。而西半球缺乏牛马(或者其他大洲的骆驼、大象)这样的驮重役畜,因此当地经济、社会与欧洲差别巨大。
由此造成的经济与文化影响更大:西半球没有出现带轮子的车。虽然轮子被看作人类进步史上里程碑式的发明,但轮式车辆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役畜来拉动车子。玛雅人创造出了轮子,但不过是被儿童当玩具玩。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发明轮子的智力。在机械化运输方式出现以前,没有拉动车子的役畜,轮子的经济价值就几乎为零。
陆地上缺乏能驮重的役畜甚至会影响海上运输的经济可行性。欧洲人到达西半球的时候,北美洲和南美洲均没有能与欧洲船只相较的大船,更不用说和早先中国制造的更大船只相提并论了。大船是否具有经济价值,取决于是否能够将陆地上的大批货物从近海的海港和内陆腹地汇集装运上船,以及到达目的地港口后是否能够将货物卸船分装运到内陆地区。
如果没有役畜来完成这一任务,就会限制船只的大小,因为更大的船只无法带来经济效益。在西欧人到来前,西半球的水上贸易主要用独木舟这样的小船来完成。
这意味着美洲土著的经济活动范围和文化广度比欧洲人、亚洲人和北非人都要小得多。有了大型役畜,舶来品才能跨越数千英里的欧亚大陆,而且能通过大型船只从水路运输数千英里。
这些进口物品包括许多发源于亚洲的东西,比如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船舵、马镫、漆布绝缘管、棋以及被欧洲人称作阿拉伯数字的计数系统(阿拉伯人将这样的计数方式带到了欧洲,这些数字事实上发源于印度)。这些在亚洲创造的东西也都变成了欧洲文化的一部分。中东和北非的知识也传入欧洲,包括北非摩尔人在他们侵略并占领西班牙后带来的农业和建筑知识。
当英国人遇到北美东海岸的易洛魁人时,这两个种族掌握的心智与物质资源都绝不限于他们自我发展的那部分。首先,英国人能够跨越大西洋航行,使用的罗盘、操作用的船舵、记录用的纸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做数学计算用的是来自印度的计数系统,使用的字母是罗马人创造的,最终在战斗中占据优势靠的也是中国人发明的火药。
文化域同样重要,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牲畜是影响文化域大小的因素之一。西半球土著面临的文化障碍并非他们独有的困境。类似的障碍同样限制撒哈拉以南非洲能接触的文化域,以及澳大利亚土著接触的文化域。
全世界落后群体面临的障碍是隔绝于世,他们生活在山地、远离大陆的岛屿或沙漠,
因此与世隔离,无法接触外部世界。缺乏牲畜同样使生活在相同环境的人相互隔离,即使 相距不远的群体,彼此也很少交流。
除了在跟外部世界沟通上有障碍,撒哈拉以南非洲内部也存在巨大的障碍,使人们无法相互交往。缺乏可航行的水路只是障碍之一。裂谷和丛林也使当地土著相互隔绝。并且,热带非洲泛滥的舌蝇携带的病菌对牲畜而言是致命的,使得热带非洲难有大型役畜,也就给本地的运输与沟通造成了障碍。非洲人在头上顶着东西的习俗,也反映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即当地很少有马或骆驼这样能够更高效地运送货物的役畜。
造成热带非洲相互隔绝的另一个文化因素是语言多样性,相对于人口规模而言,当地方言众多。虽然非洲人口比欧洲人口多出50%,但非洲的语言种类是欧洲的9倍。非洲的语言数量是亚洲的90%,而亚洲人口接近非洲的4倍。语言多样性不仅是文化隔绝与隔离的表现,更是将非洲人相互之间以及将他们与外界隔离开来的原因。
不论是在西半球还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隔绝都不是绝对的,但他们所接触的文化广度难以跟欧亚或北非相比。在欧洲人于西元18世纪到达澳大利亚以前,当地土著生活在一个地理环境更绝望且与世隔绝更严重的状态中。
在欧洲人抵达前,澳大利亚比撒哈拉以南非洲或西半球更缺乏役畜。当英国人在18世纪到澳大利亚时,当地完全没有可做役畜的动物,就像欧洲人在15世纪抵达西半球时,也没有见到可做役畜的动物。当然,安第斯山区有美洲驼作为驮畜122,但是美洲驼不够大,无法像马那样骑行,它们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在高山上的稀薄空气中驮重物。
澳大利亚还有一些其他的严重地理障碍。在现代运输方式出现之前,这个巨大岛屿孤零零地位于南半球,远离亚洲大陆,也远离其他有人居住的大洲。澳大利亚的土地很贫瘠,内陆大部分是沙漠,降雨甚至不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稳定。有很多月份无降水,紧接着却是倾盆大雨。澳大利亚内陆沙漠地区常年无雨,到了夏季又会下起暴雨,这种环境不利于农业发展和植被自然生长。
在我们还能够更坦率地谈论不同群体的不同成就的年代,有一项关于世界地理的学术研究发现,“非洲黑人的经济和文化成就总体上超过澳大利亚和美拉尼西亚的黑人”。当欧洲人在18世纪到达澳大利亚时,当地土著没有铁器,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土著早在1000年前就开始使用铁器了。特别要指出的是,澳大利亚是世界上铁矿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我们再一次看到,地理因素不仅是直接提供天然财富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作为推动或阻碍人们接触更大文化域的因素。只有在更大的文化域中人们才能获得知识,也才能将自然资源转化为财富。
此外,澳大利亚土著缺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黑人熟知的畜牧和多种耕种知识。要获得这些知识需要具备相应的物质先决条件及相应的地理环境,因此澳大利亚土著已经远远落后于生活于优越地理环境中的群体。即便是在20世纪初基因决定论盛行的年代,也不是所有人都把澳大利亚土著的落后归为基因因素。
澳大利亚的很多土壤非常贫瘠,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铁矿和钛矿等。现在,该国在自然资源上已经是世界领先的出口国。这些自然资源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对于当地土著毫无用处,因为后者无法接触到科学知识,而这些科学知识在欧亚大陆、中东、北非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发展。
疾 病
欧洲人在知晓西半球存在之前的数千年,就已经知道有非洲这样一个大洲。但欧洲人先在西半球建立了欧洲帝国,之后又过了数百年,到西元19世纪晚期才开始抢夺非洲,并将殖民帝国扩大到整个非洲大陆。**造成两个大洲命运不同的重要原因是疾病。当欧洲人侵占西半球时,微生物站在了欧洲人这一边,虽然当时的人们对微生物一无所知;而到了奴役热带非洲时,微生物站在了热带非洲土著这一边。 **
【注:这个主要是基因因素。】
欧洲人的文化域比西半球大得多,这也意味着欧洲人具有更大的疾病范围。亚洲的疾病横跨数千英里,随着欧亚大陆陆上和海上贸易传入欧洲,不时造成流行病爆发。这就使得很大一部分欧洲人死于流行病,例如西元14世纪的黑死病在欧洲部分地区造成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受亚洲致命疾病侵袭后,幸存者体内会形成生物抗体,抵抗这些疾病及欧洲本源疾病。
当欧洲人在西半球与当地土著相遇,他们或战斗,或处于和平状态。双方均不知情的微生物引发的疾病“击倒”了当地土著,欧洲人却不像当地人那样易受微生物攻击。
欧洲人携带的疾病在当地人群中扎根之后,会扩散到整个地区,无论当地土著是否接触过欧洲人。当皮萨罗的军队向印加帝国首都进军时,城内从未见过一个欧洲人的土著居民正在慢慢死于来自欧洲的疾病。据说一位友善的西班牙神父以传道为使命,在西半球穿行布道,结果因他而死的当地土著比最残暴的西班牙占领者杀死的人还要多。由于缺乏生物抗体,西半球某些区域的本土部落有一半甚至更多人死于欧洲疾病,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注:传教和传道能等同吗??烂翻译!!!这个是个看待基督教的重要视角。136Francis Jennings, The Invasion of America: Indians, Colonialism, and the Cant of Conquest (Cha 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6), p.22.】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热带疾病对于外来者则是致命的。曾有一段时期,热带非洲白种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不到一年。随着医学发展,欧洲人得以治愈这些疾病,并改善公共卫生,防御这些致命疾病,他们才有机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建立殖民帝国。他们迅速征服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显然表明热带非洲土著的防御能力并不如看不见的微生物那样强大,后者曾在长达几个世纪中阻挡了欧洲征服者。我们再一次看到,特定的环境并不会带来特定的结果,是环境与变化的人类知识——在这里是医学知识——的相互影响带来了这种结果。
在非洲,热带以北和以南的情况也不同。17世纪中叶,欧洲人开始在今天的南非共和国定居,该国大部属于南半球温带地区。古代罗马人就将大部分北非纳入罗马帝国,这一区域属于北半球的温带。地中海沿岸的欧洲人和北非人之间不存在什么决定性的疾病障碍。某一阶段,一方可能占领了另一方;而下一阶段又可能反过来。北非的摩尔人在中世纪侵占并控制西班牙长达数百年,他们的统治留下了许多物质遗迹和文化遗产。几个世纪后,拿破仑说:“非洲起始于比利牛斯山。”这一山脉正是法国和西班牙的边界。
**在热带非洲,带给动物毁灭性影响的疾病也造成了当地人的相互隔离。由于这些疾病,非洲的动物无法作为役畜使用,既无助于人们的交往联系,又无法在农耕中起作用。 **
区 位
即使不考虑区位所特有的特征,区位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因素。希腊邻近农业发达的中东,这给予它历史性的机遇,使之能够对西方文明和世界做出知识性贡献。
对日本这一岛国而言,与中国一衣带水意味着日本能够接触在数个世纪里都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华文明。例如,日本在中国文字基础上改良创造出自己的文字。这样日本早于亚洲其他国家或世界其他地区成了识字的民族,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周边没有更先进的文明。与大社会相比,小社会由于相互隔绝,靠自身发展书写文字的动力更弱。大社会地域广阔,有无数商业和其他方面的交往,远距离的沟通仅仅靠语言无法有效完成。
沿海地区相对于内陆,或者平原相对于山区的优势都是区位造成的,这种优势在全世界都很普遍。在大批欧洲人移民美国的时代,来自俄罗斯或奥地利的波兰移民——当时波兰被这些帝国吞并——绝大部分是非技术工人,而来自普鲁士地区的很少的一部分波兰移民则掌握专业性工作所需的技能,如纺织工、裁缝、木工,他们接触到德国文化并学会了这些技能。
在欧洲殖民时代,被占领地区的人们有机会接触学校之类的西方机构,这使得他们相对于其同胞具有很大的优势。例如,英国传教士在斯里兰卡这个岛国上选取条件较好的位置建立学校,而英国官方指定美国传教士到该岛条件差一点的北端泰米尔少数群体聚集的区域开设学校。美国的教会学校更专注于科学与数学教育,因此泰米尔人精通这些学科,他们在需要这些学科训练的职业中也表现得更好。一项研究发现,在大学入学考试中,成绩为A的大多是泰米尔少数群体。
尼日利亚的伊博人生活在资源禀赋更差的南部,曾被当作奴隶,但他们抓住了西方教会学校提供的机遇,而北部的尼日利亚人则拒绝基督教传教士办的学校。于是越来越多的伊博人从事专业性、管理类以及商业性等职业,比北方尼日利亚人要更多,甚至在尼日利亚北部,这些职业也主要由伊博人担任。
大西洋和太平洋使美国隔绝于世,也使其免遭战争之灾,而同一时期的欧洲和亚洲受到战争的重创,于是美国能够享受发源于欧洲的文化,而不必像欧洲人那样经历破坏性战争。在这种相对和平的环境中,美国发展出了其特有的生活方式。与此相反,地中海岛屿,如西西里岛和马耳他岛,他们处于相互争斗的国家与帝国之间,那些国家长期争斗,主战场常常在这些岛屿上,留下了破坏与占领的遗迹,并从文化和基因上改变了岛上的人口。
尽管相对于地中海诸岛屿,英国作为岛国离最近的大陆还更近一些,幸运的是,它并 不在相互争斗的帝国交火范围内。而且相对于风平浪静的地中海,英吉利海峡波涛汹涌, 是阻挡入侵者的绝佳屏障。
当然,作为屏障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毕竟,古代的罗马人和将近一千年以后的诺曼底人都曾攻占英国。在1066年被诺曼底人占领过后,英国变成了一个发达的联合王国。自此之后的接近一千年里,英国都未再遭受入侵。在这一时期,英吉利海峡也使得英国不必像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那样,维持大规模的常备军。这就使它免于大规模常备军带来的军费开支和政治威胁。
区位不仅对于英国整体来说很重要,对于其内部各部分亦是如此。欧洲大陆的国家长期领先于英国,而英国距离欧洲大陆足够近,使其可以与欧洲邻国贸易并获得领先的技术。英格兰离欧洲海岸最近,受益也最大,其他地区——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受益相对慢一些,这种益处具有传递性,也具有滞后性。直到英格兰超越欧洲大陆邻国,引领整个世界进入工业革命。
类似于其他地理特征,区位也是不均等的。整个民族、国家和文明的命运可能取决于在正确的时间是否处在正确的区位。而何为正确的位置在不同的时代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第3章 文化因素
倘若我们从经济发展史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文化造就了几乎全部差异。看看由移居国外的少数族裔创办的企业,不论是东亚和东南亚的华人、东非的印度人、西非的黎巴嫩人,还是遍布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犹太人等,他们创办的企业往往都很成功。可见,文化作为内在价值和态度指引着人们的行动,这一点让研究者震惊。——戴维·S.兰德斯1
地理会产生影响,但也不是命定的。地理主要通过影响不同物质环境下的人所接触的文化域的大小,来间接影响收入与财富。列举一地富集的自然资源,如沙特阿拉伯的石油 或南非的黄金,对于判断该地区的人均收入是一个糟糕的指标。 正如2014年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谈到尼日利亚时所说的:“虽然在石油储量上很富有,但在其他方面极度贫穷。”2
开发自然资源转化成真正的财富,要以文化为前提。缺失这种文化,未加工的自然资源将毫无价值。我们今天使用的自然资源在山顶洞人时代更丰富,但从文化上讲,史前时代的人还不懂得如何利用大部分资源。
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知识,我们就无法对物质资本进行操作、维护、修理,也就无法在它损坏后进行替换,这些物质资本也将毫无价值。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国家的物质资本遭到了大规模破坏,但短短几年之内,西欧就实现了经济复苏。我们通常将西欧的迅速复苏归功于美国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于是在接下来数十年里给第三世界国家 政府提供了大量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期望获得类似的经济发展,但这些政府援助最终都没有带来类似西欧的经济复苏。
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文化先决条件——人力资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欧的人力资本就已经创造了物质资本,这些人经历战争活了下来,并在战后重新创造了物质资本。这样的人力资本已经在西欧发展了好几个世纪,而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具有非常不同的文化, 他们不具有这样的人力资本,也不能在一夜之间产生这样的人力资本,甚至经过几十年也无法创造出来。
第三世界国家在经历灾难后,不是重建他们原有的社会,而是要构建一个西方式的经济体,但这些国家缺乏西方世界历经数个世纪的特有文化演化过程,而正是这种文化才促成了西方经济模式。
【注:人力资本包括天赋和能力,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这篇很重要,故全部摘录,方便以后翻阅。这里可以很好的反驳左衽的许多谣言。比如华人重视亲缘关系,不是不能建立契约社会,而是这样的“信任半径”能降低成本。】
文化与环境
当我们试图解释不同国家、不同种族或不同文明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成就差异时,一些人主张心智潜能在基因上的先天差别造成了这种差异3,另一些人则争辩说,它们源于生存环境的差异。两种观点似乎认为,可以把差异的成因归为两类:遗传与环境。事实上, 这两个术语的定义过于简单,似乎只要不是遗传因素,就是环境因素。但对于那些拒绝接受基因决定论的人,这是否意味着一个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取决于美国社会特有的环境因素?这样一来,美国社会就应当受到称赞,还是受到指责?
来自全世界的无数证据表明,事实绝非如此。许多族群拥有独特的文化,不论生活在哪里,他们都会将文化带到居住地,即使那是一个文化上完全不同的社会。以德国人为例, 不论他们生活在德国、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还是美国,数个世纪以来都拥有特殊的技能和特别的生活方式。文化不仅包含习俗、价值和观念,还包括技能和天赋,后两者被经济学家称为“人力资本”,能直接影响经济结果。
德国人擅长的技艺之一是制造钢琴。北美殖民地的第一批钢琴是由德国人制造的,他们同样是澳大利亚、法国、俄罗斯和英格兰钢琴制造业的先驱。在20世纪上半叶,世界 领先的设计相机镜头的光学公司都是德国的,包括蔡司、施耐德和福伦达公司。当时美国 领先的光学公司是由两个德国移民鲍施(Bausch)和龙泊(Lomb)创立的。
德国人还拥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且历史悠久。罗马军团、沙皇俄国以及南美都有德国将军,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中也有德国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分 别领导美军在欧洲作战的潘兴(Pershing)和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均有德国血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统领美军的高级指挥官中,还有许多人拥有德国血统,包括指挥太平洋舰队的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茨(Chester Nimitz)和指挥轰炸机将大半德国炸成 废墟的卡尔·安德鲁·斯帕茨(Carl Andrew Spaatz)上将。中世纪时,条顿骑士军团占 领普鲁士,此后几个世纪普鲁士便一直是德意志军事力量的核心所在。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给敌军造成的伤亡远多于自身的死伤。
德国人的社会模式不止出现在德国,在文化环境完全不同的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德国的文化传统之一是重视教育。幼儿园发源于德国,研究型大学也是在德国发展起来的, 后来被美国效仿。19世纪的德国是欧洲最早提供免费义务教育的国家之一,人均拥有的教师数量居欧洲第一,国民收入中用于教育的比重也最高。
当德国人移居他国,这种对教育的重视依然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即使在那些主流文化缺乏对教育热心投入的国家中也是如此。例如, 19世纪定居俄罗斯的德国人绝大多数有读写能力,而同期大部分俄罗斯人还是文盲。9 19世纪,当德国人在巴西作为拓荒先驱建立农庄社区时,他们在森林的空旷地带最早建的总是学校10,而直到20世纪初,大多数本土巴西人还是文盲11。1900年,奥地利帝国中10岁以上德国男性的文盲率仅为5%,而波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以及罗马尼亚男性的文盲率则分别为45%、67%、71%。12
19世纪罗马尼亚建立切尔诺维茨大学时,德国学生人数超过罗马尼亚学生,教授也大多是德国人。131802年沙皇俄国政府在爱沙尼亚建立了一所大学,而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 间里,这所大学中的学生和教员大多数都是德国人。14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市,德国人占 该市人口数还不到四分之一,教学中使用的却主要是德语。15
许许多多的民族都会将他们独有的文化带到移居地,德国人只是其中之一。对这些民族而言,不同于母国的宏观环境对于他们这个群体的经济或其他成果并非决定性的因素。 我们如何定义“环境”十分重要。这不是简单的语义预设问题。 倘若我们将“环境”简单定义为周边情形,那么我们将无法解释同样环境下文化背景不同的群体在收入与财富上的不平等。
为了解释生活在同一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在收入与财富上的巨大差距,我们可以将“环境”定义为发生在一个群体周围的事情,而“文化”是群体内部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将环境定义为所有非基因因素,那么某一社会中的不同族群的不同文化都会被归为该社会的 环境因素。倘若我们要得到一致或合理的结论,我们就无法在环境的不同概念间任意转换。
除了德国人,其他族群也会将各自的文化带到他们的移居地。其中包括东南亚各国和西半球的华人16,西非、澳大利亚、北美洲和南美洲的黎巴嫩人17,以及欧洲、中东、西 半球和澳大利亚的犹太人18,还有在除南极洲以外各大洲的印度各族群19。
这些族群的文化各异,我们没有理由期待他们在收入或财富上一样多——无论是在这些不同族群之间,还是相对于移入地的当地人。实证数据也显示不存在这种均等。这是一个文化问题,无关这些族群在到达移居国或移居地时拥有的最初财富。有那么多族群在移居某地时比当地人穷,但最终却比后者的经济水平要高。
东南亚各国以及美国的华人是一个典型。作为第一波移民,他们抵达移居地时身无长物,只有努力工作赶超他人的意愿。数百年前,这些来自中国的贫穷移民所受的教育很少, 对于他们将要前往的国家的语言与风俗也知之甚少。
东南亚的华人在法律或现实中很难享有与殖民统治者或土著相同的权利。例如,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西亚,殖民政府为马来人的子女建立学校,提供教育机会,而华人则 需要自己建立学校。20在19世纪的美国,华人经历了漫长且痛苦的历程,概括地说,华人 的遭遇可以说比东南亚人还不如。21在秘鲁,中国劳工被关在有守卫的岛上,在令人窒息 的高温与恶臭环境下工作,负责将鸟粪装进麻袋,作为肥料出口。那里的守卫不是为了防 止中国劳工从岛上逃走,而是防止这些人因无法忍受而选择自杀来获得解脱。22 在19世纪,此类绝望境地使得中国移民的自杀率很高。这种自杀有时在中国沿海港口 城市澳门(当时被葡萄牙人占领)就开始了。23许多中国人在澳门被诱骗或中计被扣押, 被当作包身工,通过兼做奴隶贸易的船只运到世界各地,其中有无数人被送到西半球。他 们大多数都是青壮年,但在严酷的工作条件下,被送往古巴的华人大多在履行完他们的8年劳工契约之前就死掉了。24在19世纪的某个时期,被送往古巴的华人中,有上百人死于自杀25,数千人劳累至死。
尽管19世纪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并不是来自澳门的包身工,但他们在美国的境遇同样悲惨,直到20世纪中期,华人的自杀率仍接近全美国平均水平的3倍。26
经过数代人的奋斗,美国华人移民已经变得富有,他们克服了诸多障碍,包括别人制造的障碍和他们自身面临的障碍。19世纪的中国移民到美国时多数又穷又没有受过教育, 这是他们必须克服的困难,他们做到了。但直至21世纪,来自中国福建省的不少新移民初 到美国时仍然很贫穷,这一直都是个问题。
像他时他地的其他移民一样,来自福建省的华人在美国的分布也不是随机的,他们集中于自己的社区,比如纽约的布鲁克林华人社区。有人这样描述这些福建人,“他们非常穷,4个人住一间屋子,一日三餐都是米饭,用汽水罐来装调味品”,他们“把自己塞进 像集体宿舍一样的房子里,每天疯狂地长时间工作,做服务员、洗盘子、在旅店打扫房间, 把他们讲中文的孩子送到这个城市的公立名校读书,然后还要供他们读大学”。27
有人开玩笑地说,这些福建人学会的第一个英文单词是“Harvard” (哈佛),第二个是“Stuyvesant” (史岱文森)——这是纽约的一所老牌公立高中,申请者众多而通 过者很少。被纽约市老牌公立高中录取的学生大多来自中产阶级或更高收入的社区,却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福建人居住的低收入社区。福建人会为自己的孩子请家教,帮助他们在 老牌公立高中的入学测验中取得好分数,以便进入好大学,并在毕业后有个好生活。28
【注:老移民还是很有奋斗精神的!】
类似的还有犹太人,特别是在美国的犹太人。他们大多数在19世纪末从东欧来到美国,在移民中也属于最贫穷的群体之一。他们定居于纽约下东区人满为患、卫生条件很差的公寓里。男人通常从街边小贩做起,而妇女和小孩则在家里用缝纫机做些服装计件工作,工作条件就像血汗工厂,缝纫机从早到晚沙沙作响。29
尽管犹太人有悠久的尊崇学习的传统,并且世界级的犹太学者在19世纪和20世纪层出不穷,但早期东欧犹太人在美国的崛起并非通过教育。20世纪初抵达美国的犹太人大多数都受过教育(在某种语言环境中),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能熟练使用英语。有关这些移民的研究指出,他们掌握意第绪语或希伯来语的读写,而这一点仅意味着他们能参与犹太文化活动,但是这两种语言都不是美国经济环境中被广泛使用的语言工具。30
1911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波兰犹太人的后代有三分之二落后于同龄人应当取得的学业水平。3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波兰与俄国裔的美国士兵(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 在美国陆军的智力测验中都得分很低,以至于智力测验研究的先驱、学术能力测试SAT的发明者卡尔·布里格姆(Carl Brigham)宣称,军队测验结果驳斥了“犹太人非常聪明” 的流行观点。32
【注:早期犹太吹还满搞笑的!智力测试多种多样,不一定能反映人群的平均智商。】
若干年后,当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掌握了英语,他们的智力测试得分便高于全美国平均水平。33布里格姆也收回了先前的结论。随后他又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与测验的犹太士兵许多来自不说英语的家庭。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之前的结论“毫无根据”。34
犹太人最初在美国社会的爬升并非通过教育,而是在商业上的崛起,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就有的很一般,有的则很显赫。随后犹太移民开始在教育上促使子女取得成就,越来越多犹太人在职业上取得提升,成为物理学家、律师等。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医疗还是律师行业,机会之门并非总是向犹太人敞开。当时,犹太医生和律师可以在犹太人或非犹太人社区为私人服务,却无法进入医院和顶级律师事务所。在学术领域,各类学院和大学接收的犹太学生都有名额限制,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犹太人教授也非常罕见。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阻碍取消后,有大量犹太人完全符合 条件进入这些机构,其所占比例甚至高于犹太人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
黎巴嫩移民的历史与犹太人类似。就像从东欧迁居美国的犹太移民一样,最早移民到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或西非的黎巴嫩人教育水平也较低。他们最初也是靠商业上的成功才兴起的,典型的从底层的小摊小贩起家。
20世纪初移民到巴西的黎巴嫩人的文盲率达29%。35而同期移民到墨西哥的绝大多数黎巴嫩人没有完成小学教育,这些黎巴嫩移民经常要花好几个月才能找到一个会读写的人, 给他们阅读黎巴嫩寄来的信件,并帮助他们回信。36最早移居澳大利亚37或西非38的黎巴嫩移民大多也是文盲。
在非洲的塞拉利昂,克里奥尔人瞧不起黎巴嫩移民,因为他们未受过教育,而且很贫穷。但黎巴嫩人的处境很快就得到了改善,当他们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后,克里奥尔人的轻蔑变成了愤恨和敌视。39
就像移居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移民一样,黎巴嫩人的移出地并不是随机的,他们选择的移入国定居地也不是随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移居塞拉利昂的黎巴嫩人大多数都不是来 自贝鲁特这样的大城市,主要是来自小村庄的农民或低技能工人。40简言之,他们来自黎 巴嫩的小范围内的特定地区,他们在塞拉利昂也聚居在非常狭小的特定区域——什叶派穆 斯林聚集在一个地方,东正教徒在另一个地方,来自黎巴嫩某一地区的马龙派基督教徒在 一个地方,而同为马龙派但来自黎巴嫩另一个地方的则聚居在其他地区。41人们的行为不 是随机的。尽管在学者和其他人看来,这种非随机结果即便不是可疑的,也是非常奇怪的。 不论在西非、北美、南美,还是在澳大利亚,黎巴嫩移民通常从小摊小贩起家。42他 们跟随犹太摊贩的步伐,在巴西他们就是这样做的。43成功的摊贩会自己开设小商店当老板,而新一波移民又会接替他们,当起小摊贩。甚至那些大型知名企业也都发端于低档地摊,如犹太人创办的梅西百货、布鲁明代尔百货、李维·斯特劳斯公司,黎巴嫩人创办的哈格男装公司、法哈服装。其中的关键在于坚持不懈,这一点和其他从贫穷到富有的人群一样。
黎巴嫩人大规模向美国移民始于19世纪末,大多数早期移民都是从流动摊贩起家的,包括妇女和儿童,而这种黎巴嫩摊贩构成的网络遍布全美国。44黎巴嫩摊贩积累资本,慢慢安定下来,会开一间小货店,而且往往是家族企业。每天营业16~18个小时,孩子整理库存并送货,偶尔妻子在忙完家务后会替换丈夫看店。他们的家就在商店隔壁或者在楼上。 45
这种模式普遍存在于塞拉利昂的黎巴嫩人46、东南亚的华人和美国的犹太人中间。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成长于自己家开的家庭商店。在他的描述中,这种情况在那个年代的美国移民家庭中很常见。47黎巴嫩人的小孩在很小的年纪就要求参与家庭生意,并恪守家庭生意的要求:
学龄儿童在不上学的时间,要待在父母身边,招徕顾客、找零、码货,学习如何在资源贫乏的情况下经营一项独立的生意。他们被灌输了重要的经验,即父母的工作、节俭伦理以及家族团结与克己对实现家族目标最为关键。48
一代代黎巴嫩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渐渐崛起。早期黎巴嫩移民大多数从事的都是商业,不论在阿根廷49、澳大利亚50、塞拉利昂51、加勒比诸岛52,还是美国53。但是,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后,他们让子女接受更多教育,去上大学。这种情况在黎巴嫩人定居的其他国家也如此54,越来越多的黎巴嫩新移民开始接受更好的教育。
对黎巴嫩人、华人以及犹太人来说,即便他们最早一批移民的教育程度很低,但他们的祖国在文化传统上都高度重视教育。这样一来,只要经济条件好转,他们肯定会让后代接受更多的教育,他们的眼界也就从商业扩展到医生、律师、科学家这些职业,这些群体大多数都是这样做的。
发生在华人、犹太人和黎巴嫩人身上的这种向上流动模式肯定并非唯一的模式。在古巴革命战争期间,许多专业人士和商人逃到了美国,主要聚居在佛罗里达附近,但是他们的大部分财富却无法带出来,并且他们的教育文凭和职业资格也得不到美国的承认,因而无法从事原来的职业,这些难民发现自己一下子跌到了社会最底层,就像一位前会计师描述的:“他们挤进小公寓里,变成了洗碗工、锅炉工、西红柿采摘工。”55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成功故事中包含着辛劳的工作、被吞噬的荣耀、为了下一 代的牺牲付出。以前的管理者现在替人泊车,法官在刷盘子,医生送报纸。从不工作的妇女做起了织工、旅店保洁工,或在迈阿密河边的仓库里分拣鱼虾。工作如此之苦,她们说 简直像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就像一位难民说的:“即便我要做两份工,我也决心让我的孩子成为中产阶级。我就这样一直做了14年。”56
【注:为了后代努力才是努力奋斗的不懈动力啊!】
这些古巴难民在1959年逃到美国时,成了美国社会的最底层。但到了1990年,他们的孩子每年收入已经超过5万美元,是美国白人的2倍。在这些古巴难民抵达美国40年后,古巴裔美国人掌握的商业总收入甚至超过整个古巴的总收入。57与此类似,1994年以前,570万海外华人创造的财富与10多亿中国人几乎相当。58
所有这些再一次将我们带回这个问题:当我们提到“环境”时,我们指的是什么?如果环境指眼前的周围事物,那么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在同样环境中生活的其他族群,也许在总体上经济水平甚至更高一些,却无法像纽约的福建籍华人一样让他们的孩子进入这个城市的精英公立高中;本土出生的美国白人为何收入会低于古巴裔美国人。
倘若我们把“环境”看作包含了引导福建籍华人为了他们子女的教育做出非凡牺牲,或古巴裔美国人付出超常努力使自己的家庭摆脱经济底层地位的那种文化价值,那么这些情形将不难理解。并非所有族群都拥有相似的文化驱动力,这样一来这些非同一般的族群能够获得成功也就不难理解了,但同时我们若还期望其他族群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功,不免会得到令人气馁的结果。
【注:这种说法其实是有幸存者偏差的角度在里面的,毕竟如果混得不好,直接就绝种了!】
文化扩散
外来者试图改变他人文化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失败史。欧洲基督徒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迫使犹太人改变宗教信仰,最终都失败了;沙皇的“俄罗斯化”运动也没什么效果,却造成了更多的不满。但文化扩散也是存在的,有些族群、种族、国家和文化为了自身利益,自我选择且自定速度,大规模从他人那里引入特定的文化特征。
西方文明用阿拉伯数字取代罗马数字,即使在曾属于罗马帝国并保留传承了罗马文化的那些国家也不再使用罗马数字。这种变化是整个西方世界自发决定的,不是阿拉伯人或印度人劝说的结果。阿拉伯数字更便于数学运算,虽然文化多元主义者仅认为它与众不同。 以哥伦布出发向西半球航行的年份为例,用罗马数字表示为“MCCCCXCII”,可以看到有多不方便,也难怪数学家有异议。
【注:本人确实好奇欧洲以前的原版书籍中的数字长什么样,那些远超当时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数学公式到底是怎么表达出来的呢?《从一到无穷大》的作者戏谑了一把50万。】
这里要说的是,基于实用目的借鉴引入外来文化古已有之,历史上曾大规模出现过。我们前面提到,亚洲的许多文化特征在数个世纪中不断传播到欧洲。类似的文化扩散也发生在欧洲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几个世纪里,铸币、城堡、街道、印刷机、纺织机、疫苗 接种、铁路和汽车从西欧传到东欧。59但就像外来者强加改变本土文化大多失败了一样, 外来者为延续特定族群文化特征的生命力,将其当作博物馆藏品一样保存下来,反而是在 帮倒忙,特别是对于经济或其他方面落后的族群更是如此。
并非所有族群、种族、国家或文明对于外来的先进文化都会同等地接纳并吸收。不同族群接纳度上的差异也是他们的文化差异之一。我们已经知道,地理或其他障碍会阻碍某些族群和国家的进步,在某些情况下,从地理环境更优越的地方引入已经取得的进步,能够克服这些障碍,而运用和改进这些进步,能够产生经济或其他方面的益处。
【注:有选择的吸收才能够更好地保卫自己的文明,正像细胞膜对物质进行选择性吸收才能保持细胞体生存。】
有些国家幸运地拥有地理优势,因此能够引领历史发展,但日本并不具备这样的地理优势。古代中国拥有众多优良的天然港口、密集的可供航行的水道,北方又有良田沃土。 相比之下,日本国土面积小得多,河流流经的范围小、落差大,水流湍急地流向大海,因 而河流不适于航行。60且日本又多山,仅有一小部分土地比较平坦适合农业耕作。61日本 最大的平原不过120英里长。62此外,日本的自然资源也很匮乏。
考虑到这些地理障碍,当中国在许多方面领先于世界时,日本的经济水平长期落后于中国也就不奇怪了。紧邻海洋,因此可以与外部世界交流,这是日本少数地理优势之一。 另外,这些沿海地区占了日本国土面积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日本所有地方离海的距离都不超过70英里。63
这意味着一千多年里,日本在物质空间上可以接触更先进的中国文化。更重要的是, 日本在文化上也接纳了中国文化。日本不光改良汉字,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而且接受了中国的儒家哲学和世俗事物,学习种植棉花和纺纱织布的技术。64
从1638年到1868年的两百多年里,日本实行闭关锁国,禁止移民,并处死违反禁令的人。在这期间,身处国外的日本人也被禁止回国。东亚史领域的著名学者研究说:“17世纪初,日本在某些技术和制度上与欧洲并驾齐驱,甚至在某些方面还稍有领先,但此后却由于闭关锁国而彻底落后了。”65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孤立主义伤害了日本。
美国海军将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在1853年率领美国舰队侵入日本,打破了日本与世界联系的障碍。佩里能够驶入日本海域而不受惩罚本身就显示了日本在当时的脆弱和落后。佩里将一辆火车作为礼物献给日本,从民众的反应也能看出日本的落后:
起初日本人躲在安全距离外,有些惶恐地瞧着这辆火车,当引擎发动时,他们惊呼起 来,倒吸了一口气。不一会儿,他们就走近来观察、拍打它,并爬了上去。一整天他们都 在做这样的事。66
佩里将军代表美国进入日本之后,日本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度非常高,近乎奉承。美国尤其受到推崇,被描述为“地上的天堂”。67对美国的积极描述是对西方人和西方国家描绘的一部分,日本人眼中的西方国家既是值得羡慕的又是伟大的。①
我们可以用人均购买力来表示19世纪日本的经济水平, 1886年日本的人均购买力是英国的1/40,到1898年,日本的人均购买力极大地提高了,为英国的1/6。68通过大规模引入西方技术,邀请技术专家到日本传授这些技术,并将日本学生送出国到西方大学学习, 日本成为与西方领先国家并驾齐驱的世界大国之一。1886年,日本儿童入学率不到1/2, 但到1905年已提高到95%,并在之后进一步上升。69
到20世纪初,日本人已经领先世界,不再需要外国专家,并让他们离开了。70 20世纪上半叶,日本制造了许多工业制品,尽管其中许多只是模仿西方产品,质量不是很高,但价格低廉。到20世纪后半叶,日本人已经成为技术和质量上的领跑者,领先的产品从相机、 汽车到电子产品。
在相机产品方面,这种演进最惊人。第一部尼康相机明显是模仿名叫“康泰时”的德国相机,而第一部佳能相机也是世界知名的德国莱卡相机的仿制品。随着时间推移,尼康 和佳能发展成行业标准制定者,它们的销量也让最初的模仿对象相形见绌。此后,日本的 高速列车也胜过了美国制造的火车。
尽管英国与日本在文化上相当不同,但作为岛国都曾长期落后于邻近的大陆(英国落后于西欧大陆,日本落后于中国),在这一点上两者是相似的。在文化上,英国和日本也比较相像,都愿意接纳吸收他国的先进方面,通过推动这些方面更进一步并最终超越曾经的领先者。
在英国内部,苏格兰人也从英格兰人身上学到许多,这种学习从接受英语开始,并最终在工程学和医学上崛起并超过了英格兰人。71从18世纪晚期直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各行各业的著名知识分子中有很大比例有苏格兰血统。其中包括哲学家大卫·休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工程师詹姆斯·瓦特、文学家罗伯特·伯恩斯和沃尔特·斯科特爵士、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等。 72一位知名的历史学者这样说:“在知识的每一个分支中,这个曾经贫穷且无知的民族培养出了众多有原创力的成功思想家。”73
中世纪欧洲从中东和北非伊斯兰世界学到了很多,特别是在数学和哲学领域,还有农业和建筑学。除此之外,当时的伊斯兰世界在军事上也领先于欧洲。奥斯曼帝国攻占了东 南欧的很大一部分,而北非的摩尔人也曾侵占西班牙。正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的:
一千年前,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这样的大城市领先于西方世界。伊斯兰教与创新 是孪生兄弟。各地的伊斯兰哈里发善于学习、宽容且会做生意,都是不断变化的超级势力集团。74
如果有人质疑伊斯兰世界在一千年前曾经达到的文化与技术高度,他应该造访西班牙科尔多瓦市的大清真寺。该寺由当时占领西班牙的摩尔人建造。就宽容而言,1492年基督教在西班牙重新夺回统治权时,他们将摩尔人赶出了西班牙,还放逐了所有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有很多逃往伊斯兰世界,而不是信仰基督教的欧洲。相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北非和奥斯曼帝国,当时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对犹太人更不友好。那时的世界显然不同于当今的世界。这种差异部分是因为当时的欧洲人对其他文化的接受度不同。
文化孤立与地理隔绝带来的影响类似,都会使个体、群体、国家或整个文明更难同步于其他地区的进步。中国曾领先于世界,其衰落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也是拒绝向他国学习。
【注: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说法。纯粹就是满清以反漢防漢为第一要务,防止漢人“偷听敌台”造大清的反。显然麻木不仁、愚昧无知的人才是大清治下的“良民”。】
15世纪初,中国政府严禁民众与外部世界接触,凿毁了大型船只。郑和曾用这些船只组成船队游历西洋,他所到之处比哥伦布的小型船队只多不少。后来,明朝政府不仅禁止出海航行,而且还禁止建造能出海的船,早先航海留下来的记录被销毁,毕竟那些郑和所到的地方只被当作蛮夷之地。21世纪的一位美国科学家评估了做出这一重大决定时中国的地位: 在此之前,中国拥有一支能够航行于大洋之上的船队,中国的船只比欧洲的任何船只都大,性能也更优越。在科学知识上,中国与欧洲旗鼓相当,而在印刷术、航海和火箭技术上则远远领先。这个决定导致中国在科技上悲惨地落后了,直到几百年后才奋起直追。 75 18世纪英格兰国王乔治三世遣使出访中国,带给乾隆皇帝的礼物包括各种展示西方先进技术的机巧。乾隆皇帝却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 国置办物件。”76拒绝其他文化的进步,没有比这更具灾难性的了。随着与西方的技术差 距越拉越大,中国在遭到西方帝国主义攻击时,也越发缺乏抵抗力。
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在所有方面强于别人,更不会一直强盛。拒绝接受他人取得的文化进步是一种自我隔绝,与地理环境造成的隔离一样有害。
语言是造成国家间文化隔绝的因素之一。俗话说“知识装在语言的行囊里去旅行”77。但并非所有语言包含的书面知识量都一样多或一样广。西欧语言比东欧早几百年发展出了 书面语,因为罗马曾占领西欧并带来了拉丁字母。因此西欧人比东欧人提前了数百年就能 读写,这意味着当东欧语言开发了书面语,他们的语言所表达的知识广度、知识量以及多样化程度都不及西欧语言。
例如,尽管爱沙尼亚人在19世纪就有了书面语,但在19世纪上半叶,爱沙尼亚语多用于宗教主题。爱沙尼亚受过教育的人使用的工作语言是德语,不论他是否有德国血统。78 这种情形并非爱沙尼亚独有。在波希米亚,用捷克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出现得更早,应用也更广泛,但到19世纪初,捷克语却衰落了。捷克出版业当时处在萌芽期,布拉格只有一小部分德语报纸发行流通。79捷克小学虽然用捷克语教学,但1848年以前,波希米亚没有一所高中用捷克语教学,学生要想上高中必须懂德语。80
在东欧,要从事科学或其他专业性工作,必须要接受德语教育。此外,由于东欧许多高级职业普遍由德国裔占据,加入这些精英职业通常要掌握德国文化,以便融入精英同事群。
在新一代受过教育的捷克人和拉脱维亚人中,许多人非常憎恨为了职业发展而改变语言和文化,而德国裔东欧人则无须克服任何障碍。没人能说这是公平的。但更根本的问题在于,这种不公平究竟是内生于当时的环境,还是随意施加到非德国裔东欧人身上的呢?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当时是德国人统治着哈布斯堡王朝,应当指责德国人不公平地对待了其他群体。类似地,罗马尼亚人统治下的罗马尼亚和俄罗斯人统治下的拉脱维亚、爱 沙尼亚以及沙皇俄国的部分地区都存在过这样的情况,某种语言占据优势地位。
更现实的问题是,在东欧各个地方,包括波罗的海地区和巴尔干地区,德国裔作为少数群体增加了还是降低了当地人口的机遇呢?从经济观点看,有德国文化色彩的学校显然对非德国裔也是开放的,所以可以作为当地人增加人力资本的资源,而用本土语言教学的学校则不具备这种条件。
东欧统治者还允许那些以德国农民为主的农村按照德国法律生活,给予这些德国人和非德国人共同生活的村庄比其他欧洲地方更多的自由。81此外,身负高超技艺的德国人也 能使整个经济体都受益,给本土人口提供更多的产品和工作。正是德国农民高超的技艺和高效的生产率,使得他们受到东欧统治者的欢迎。这些统治者提高激励,吸引他们移民到东欧。
然而,从政治角度看,许多东欧人视德国人为外来的精英阶层,主导着商业和各行业,他们的文化也被东欧人视作障碍。东欧人往往不会认为,这些德国人的到来能够为本地人 提供本国文化无法提供而只有德国文化才能提供的优势,同样也不认为,这一外来文化为东欧人自我提升提供了机遇。在拉脱维亚的知识阶层看来,他们的人民长期受到压制,处 于社会的底层。82
纵观全世界各个时期,德国人在东欧的情况并非独一无二。在泰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华人在当地属于少数人口,但在经济上更发达, 他们同样有时也会受到当地社会憎恨。83这些国家的本土居民很少愿意去接受华人的文化, 如勤劳,但大部分人却憎恨华人在教育、工业和商业上占统治地位。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形,可能是移居外国的少数群体,也可能是同一国家内具有不同文化的不同民族,他们在学校或经济中都超越本地居民。世界各地各个时期都有这样的群体存在,如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尼日利亚的伊博人、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东非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秘鲁的日本人、斐济的印度人、东欧的犹太人和西非的黎巴嫩人, 等等。
像这样,少数人口取得的成就超过多数人口,而许多国家总是在妖魔化这种成就,指责少数群体抢走了整个产业。但事实上正是少数群体开创了这些产业,在此之前,这些国家根本没有相关产业。不论这种对少数人口的不满是怎样通过政治动员形成的,它引发了斯里兰卡和尼日利亚等国家的可怕内战。将族群差异政治化不利于该国接纳更成功文化所 附带的人力资本。这只会促使人们对文化上更成功的少数人口感到不满,人们还会要求在 工作和收入上获得与人口比例相匹配的公平份额。正如一位印度族群领袖说的:“难道由 于我们不满足条件就无权工作吗?”84尼日利亚的一位族群发言人也类似地谴责过“技术 的暴政”85。
基于人口比例来确定经济利益的“公平份额”,其中隐含的假设竟认为分享财富的问题可以与创造财富的生产问题分开考虑,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忘了创造财富才是第一位的。 实际情况与他们的诉求恰好相反,驱逐生产率较高的少数群体往往会损害经济。然而这样的驱逐例子却比比皆是:20世纪70年代乌干达驱逐亚洲人8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 伐克驱逐德国人87,17世纪西班牙驱逐摩里斯科人88,以及中世纪法国和许多德国城市驱 逐犹太人89。
由此造成的经济创伤在许多国家都出现过。类似的驱逐有的是由于政府的不友好政策, 有的是由于暴徒直接施加暴力,都会导致生产率更高的少数群体逃走,就像1685年胡格诺派逃离法国90,19世纪后期犹太人逃离东欧91。
生产率更高的少数群体既能提高一国的生活水平,又可以为多数群体成员提供文化榜样,为他们获取另一种更先进的人力资本提供机会,使多数群体也能提升自我。如此看来,对少数群体的敌意是不理性的。但从落后群体领袖的个人利益出发,激起他们所领导的族群对更先进族群的憎恨,将他们族群的失败归罪于更先进族群是有利的。这样他们就可以要求分享更多经济利益,虽然创造这些经济利益所利用的技能和知识在落后族群的文化中并不常见。
换个角度看,落后群体中的个体成员学会了更先进群体的技能和文化后,就可能被吸收进后者,他们可能将不再听从族群领袖。不论更先进群体文化的各个方面能够带给落后群体怎样的经济利益,吸收先进群体的文化对于族群领袖是明显的威胁。他们把本土文化被侵蚀视作对自身领导地位的挑战和逐渐失去选民支持的原因。全世界各地许多落后群体的领袖和知识分子时不时会表达对外来文化侵蚀以及本土文化最终灭绝的担忧。92
【注:显然中国不属于这种行列。保卫我们的文明是我们必须要作出的努力,来防止人类灭绝。】
例如,18世纪曾有一位捷克学者表达了对越来越多的捷克同胞使用德语的担忧,认为这意味着在波西米亚的城市中,下一代人“将变成德国人,再过五十年,说德语的人将多 过说捷克语的人”93。
这样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一位历史学家讲到那个年代时说,“在布拉格,讲捷克语的主流是下层阶级”,尽管“捷克语还远未到消亡的程度”,但它“倒退到田间地头、马厩牛棚和厨房”。在这些地方,仆人和从属地位的人还会讲捷克语,在这个历史节点上, 捷克语“不是民族的象征,它代表了无知”94。除了护士和女家庭教师偶尔由德国人担当, 那个年代大多数布拉格人的仆人是捷克人。德国家庭大多有仆人,而捷克家庭却很少有仆人。95
到了20世纪,地球另一端的斯里兰卡也面临着同样的担忧。该国多数人口是讲僧伽罗语的僧伽罗佛教徒,泰米尔印度教徒作为少数人口讲泰米尔语。一种担忧认为,随着时间 推移,更成功的少数人口将在文化上吞噬更不成功的多数人口。1956年,僧伽罗语活跃分子对佛教高僧发出警告,“倘若你们不做点什么,就不会再有佛教,也不会再有僧伽罗人 了”96。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加拿大魁北克省。以讲法语为主的多数人口通过一项法律,严格限制英语在许多机构中的使用,甚至包括私人商业活动。这一政策的主要起草者是文化发展部部长卡米尔·劳林(Camille Laurin)。她宣称:“法语必须成为所有魁北克人的通用语言。”和其他地方一样,这样做是因为“一方面需要让讲法语的魁北克人持续关注他们的文化生存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在加拿大的经济和政治处境相对更差” 97。出于同样的原因,斐济、巴基斯坦、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缅甸,都存在过对文化灭绝的担忧。98
无论是19世纪的波希米亚,还是20世纪的魁北克,从法律上限制非多数人口使用的语言,其广度和偏狭让人费解。99但推动这种行为的族群领袖和知识阶层,他们的目的在于防止落后族群的成员在文化上被同化,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努力延缓族群同胞被经济上更发达的族群吸收同化。今天很多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尝试讲标准英语,因为社会主 流人群都在使用,他们还会吸收主流文化的教育和其他部分。这些年轻人会被贴上“举止模仿白人”的标签而受到责备,这种控诉可以将任何事情从嘲笑变成排斥或骚扰,甚至招 致同伴的直接暴力攻击。100
简言之,全世界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落后群体在接受外来文化时都面临重重障碍。18世纪的苏格兰人和19世纪的日本人对于不同文化的热情拥抱只是例外。从历史上来看,苏 格兰和日本在很短时间里迅速崛起并位居世界发展前列也是一个例外。
非西方国家的一些族群在欧洲殖民统治时期抓住了西式学校提供的教育机遇,但只有很少的族群如此,就像苏格兰人和日本人。这些族群所在的地区通常存在地理障碍,土地 贫瘠,生产的粮食养不活不断增加的人口。这些族群包括尼日利亚南部的伊博人和斯里兰卡北部的泰米尔人等,从地域上还包括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以及菲律宾等。101伊博 人和泰米尔人接受了西方教育,并掌握了其他西方文化的优势,他们分散到各自国家的其 他地区,在商业、行政部门和专业岗位上表现得都强于其他族群,在给整个国家带来益处 的同时,也由于成功而引人注目,并因此引起他人的憎恨。
文化与进步
经济进步既取决于有形的物质因素,如地理;还取决于无形的文化因素,如人力资本。后者包括被称为“信任半径”的因素,在此半径内,个人和群体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协同合作。对工作的态度以及对进步本身的态度是无形因素,这些连同地理特征和物质资本等 有形因素一起产生了经济的最终结果。有形因素给人的印象更强烈、更直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产生的经济效应比文化概念中蕴含的无形因素更强大。
文化的差异之一是个体和群体彼此间信任合作的能力。不同群体、种族、国家和文明的信任半径差别很大。这种差异深刻地影响了国家之间和一国内部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
信任与诚实
尽管信任能促成对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合作方式,但信任如果缺乏诚信必定是一场灾难。一个社会的诚实度框定了这个社会的信任半径,造成的经济影响超过许多有形优势。
例如,苏联即便不是地球上自然资源最富集的国家,至少也是其中之一。苏联也是仅有的工业国中石油储量极其丰富的国家,甚至是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国之一。它土壤肥沃, 享有盛名,并且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平原。102苏联的铁矿石储量也是世界第一,森林覆盖面积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拥有世界第二大锰储量103和世界三分之一的天然气储量104。 除此之外,在许多年里,苏联作为镍生产国也领先于世界105。在几乎所有自然资源上, 苏联都能自给自足,并且出口了大量的黄金和钻石。到1978年,全世界接近一半的工业级钻石都是由苏联生产的。106
然而,根据两位苏联经济学家的研究,虽然苏联拥有这些有形的自然资源优势,民众也接受了良好教育,苏联的经济在效率上却远远不如德国、日本或美国。107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欧、美国或日本,而日本是世界上资源最匮乏的国家之一。
如此受自然青睐的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平为何会低于许多自然资源不如它的国家呢?苏联的存在简直就是为了反驳地理决定论。抵消苏联在自然方面优势的其他影响因素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文化方面的。回到19世纪,当苏联还被称作沙皇俄国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针对阻碍其经济发展的文化障碍是这样评价的:
官员普遍贪污腐败,这制约了沙皇俄国的经济发展能力:因为官员的报酬取决于他们能否成功地让人们的烦恼翻倍,这样人们才会为免除烦恼向他们行贿。108
腐败带给经济体的成本不只是行贿的金钱或被官员窃取的钱物,甚至主要不是这些。 最主要的成本是没有发生的事——没有开始的商业活动、没有进行的投资和没有发放的贷款。在一个极其腐败的经济体中,这些经济活动的回报率必须高于个人的努力成果不容易被剥夺的经济体,这样人们才会去做。
【注:腐败最大的影响不是钱,而是败坏社会风气。此外,对于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人们往往规避非必要风险。】
19世纪晚期,沙皇政府试图让俄国经济更加现代化,并邀请西方企业来俄国开展商业活动,这些企业会雇用俄罗斯人做工人,慢慢也会雇用俄罗斯人做管理者,但他们从不雇用俄罗斯人做会计。不只俄罗斯人当会计是个问题,20世纪初的一位法国观察家曾友好地指出,俄罗斯人当管理者在经营中也会造成非常多的浪费。109在俄罗斯,“像德国人一样诚实”和“像德国人一样守时”110曾是常用语,表明俄罗斯人自身很少具备这些品质。 过去的文化差异到了今天为什么是这样的,又是如何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会迷失在时间里,但这类文化品质对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
【注:乐,北狄确实如此!】
普遍的腐败在俄罗斯延续了下来,甚至在斯大林统治下也存在。尽管有诸多惩罚——包括遭受劳工集中营的奴役。苏联经济中有一群被称作“中介者”(tolkachi)的人,他们主要为企业从事非法活动,这些企业在官方许可的有限活动中受到严格限制,很难完成莫斯科的中央计划制定者给他们设定的目标。111
在沙皇俄国时期普遍存在的腐败在整个苏联时期都没有消失,也延续到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一家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股价仅相当于美国同类石油公司股价的1%,因为“市场 预期俄罗斯石油公司会受到内部人士有组织的劫掠”。112根据一家俄国报纸的报道,要想被一些声誉卓著的高等院校录取,需要行贿1万到1.5万美元。据该报估计,每年俄罗斯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的此类支出至少有20亿美元。
【注:苏共党员普京腐败治国,符合马克思主义真理!】
俄罗斯以其自然资源富集和生活水平低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113,告诉我们有形因素的优势如何被不利的无形因素制造的障碍所抵消。当然类似情况不只发生在俄罗斯一国。普遍的腐败使得开发自然资源所需的大额投资风险过高,结果就是不论本地还 是外国投资者都不愿意冒险一试。
但是在其他情形下,信任半径能让某些特殊群体富裕起来,而且不只是在繁荣的国家,很多是在法律体系不可靠又腐败的第三世界国家。一些群体如印度的马尔瓦尔人或东南亚 华人中的小群体,即使没有合约或不具有主流社会的法律或政治制度,他们也可以彼此从事金融交易。在正式的法律体系无效或腐败的国家,这是一种独特的优势。因为它给予了 群体成员更大的信任半径,使得相对于群体外部的人,他们的经济决策更快捷,风险也更小。
在更发达的经济体中,特定群体内部的高信任度同样是一种优势。例如,纽约的哈西德派犹太人根据口头协议寄售昂贵的珠宝,并基于非正式协议共享收益。114印度的马尔 瓦尔人在国际贸易网络中也这样做115,东南亚华人的小群体也有同样的现象116。另外, 西非和西半球部分地区的黎巴嫩人小群体也有类似的贸易模式。117
虽然有些社会无法像马尔瓦尔人、哈西德派犹太人、东南亚华人或黎巴嫩小群体一样在成员之间发展出同样强度的信任感,但它们的民众也能拥有很强的诚实度和正直感,于 是它们不需要承担很沉重的成本和很大的风险就能开展许多有价值的经济和其他活动。在 缺乏这种诚实度和正直感的社会,类似的活动会受到限制。从使用信用卡到收税,社会中 所有的活动都依赖于大多数人值得信赖这一前提,法律强制的资源于是就可以被保留用来 约束人群中缺乏基本信用的那一小部分人。对于更大且更有活力的社会,这种最基本的信任是不可或缺的。
许多理论家或许倾向于抽象地讨论人群,但事实上,不论是在个体之间,还是在不同群体以及不同文化之间,有血有肉的人都有巨大差异。各类诚实度测验就显示了这些巨大差异。
2013年,研究者有意将许多放有钱和身份证的钱包放在全世界各个城市的公共场所。物归原主的钱包占所投放钱包的比例,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11/12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的1/12,不同城市差距巨大。而且,在里斯本唯一被归还的那个钱包还是来自一名荷兰游客,没有葡萄牙人归还钱包。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有4个钱包被还给了失主。118更早由美国《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策划的钱包测试发现,在美国有67%的钱包物归 原主,在斯德哥尔摩是70%,在挪威的奥斯陆和丹麦的欧登塞是100%,在墨西哥仅有21%。 119
一项研究考察了各国常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在纽约城支付他们停车罚单的情况,这项持续了5年的研究发现,各国外交官的应对差异巨大。即使不缴罚单,这些联合国外交官凭借外交豁免权也能免予被起诉。埃及有24名联合国外交官,他们在5年时间里有几千张未缴罚单,加拿大外交官的数量与埃及相同,他们缴清了所有罚单。英国和日本的联合国外交官分别有31名和47名,他们均没有未缴停车罚单。120
很多关于腐败的系统性跨国研究都发现,被评为最腐败的国家大多数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即使这些国家自然资源很丰富。121诚实不光是道德问题,作为经济因素,它影响甚大。和其他影响收入和财富的因素一样,诚实在各国及一国内部的分布,既不是均匀的,也不是随机的。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很重要,它不仅能够在物质资本遭受毁灭性破坏后帮助一国迅速恢复,例如战后重建;它在正常年代的经济进步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我们与穴居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力资本。
有些人倾向于将人力资本等同于教育。毫无疑问,教育是人力资本的一种,我们也经常粗略地用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但应当指出的是,许多人力资本是在学校之外获得的,此外一些学校教给学生的技能很多不是市场需要的,个别学校还会以负面态度、错误预期和厌恶之情等形式产生负人力资本,对经济产生不好的影响,因而学校对学生人力资本的开发贡献很少,甚至为零。鉴于教学内容不同,教育有时会让人对进入私人部门工作产生反感,或拒绝从事任何不满足“有意义的工作”这一定义的事,这里的“有意义”是指那些能够让人心满意足的工作。
开创工业革命的人大多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他们都是有实际工作技能和经验的人,而非精通科学的科学家或系统研究过工程的工程师。在正式的科技研究普及之前,工业革命已经在进行中了。甚至后来的工业先驱如托马斯·爱迪生和亨利·福特接受的正式教育也很少,怀特兄弟高中就退学了。到了电子时代,比尔·盖茨和迈克尔·戴尔均是大学肄业生。总之,人力资本不等同于正式的学校教育。
人力资本可以表现为教育之外的其他形式,教育普及也不意味着同样的人力资本普及。 21世纪的俄罗斯被称作“高教育水平和低人力资本的社会”122。从更直接的经济角度看, 俄罗斯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口大约占全世界的6%,但在全世界新专利和专利申请量中仅占0. 2%。1995年到2008年间,德国、日本和美国发明的专利大约分别是俄罗斯的60倍、200倍 和500倍,甚至新加坡这样的小城邦国家的发明专利也比俄罗斯多。123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说教育不重要。只是我们不应该笼统地颂扬教育,作为各种人力资本中的一种,教育的重要性及教育资源的配置都值得细细考察。就像其他事物一样,教育在个体、群体或国家之间也不是均等的。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甚至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士中也普遍存在较大的教育不平等。
教育的文化价值
**虽然识字对于个体、群体和国家的命运是一个根本性因素,但不同文化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同,产生的影响不只是识字率的差异。不同文化追求的教育程度有差异,而且在追求的教育类型和达到的教育水准上也有区别。只比较教育程度相同(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的不同族群,我们会漏掉教育的其他维度,错误地将教育程度“相同”但来自不同社会、不同种族或不同群体的个体在人力资本上的回报差异归因于歧视。 **
在文化上很不一样的少数群体不只接受更多教育,而且教育水准也高于周围的多数人口。这种更好的教育,可能表现为学习更具挑战性的专业,也可能表现为取得更好的学业 成绩,并且它们很普遍。在1972年斯里兰卡大学的入学考试中,成绩为A的大多是在人口 中占少数的泰米尔人,而不是占多数的僧伽罗人。124奥斯曼帝国时期,亚美尼亚学生的表现优于占人口多数的土耳其学生,他们甚至在用奥斯曼土耳其语写作上也超过土耳其学生。125
同处于一个社会的不同文化群体在教育专业选择上也有极大的差异。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大学录取学生依据的是学业,因此录取的华人学生多于马来学生,而马来人在马来西亚的人口中占多数。在数学、科学和技术专业上这种不平等更大。有一年,有1488名华人学生获得科学学士学位,马来学生只有69名;同一时期获得工程学学士学位的华人学生有408名,马来学生仅有4名。126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大学里犹太学生的比例远超过犹太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27,这样的情形同样出现在不同时期的东欧、阿根廷和澳大利亚128。在今天的纽约, 有三所老牌公立高中对学生精挑细选,它们分别是史岱文森高中、布朗克斯科学高中以及布鲁克林工程高中,在这三所高中,亚洲学生数超过白人学生,二者的比例超过2∶1。要 知道,在纽约全部高中学生中,亚洲学生仅占14%。129
经济落后的多数族群在教育数量和质量上往往也落后。被大学录取后,他们倾向于选修更容易的专业,而不是数学、科学和工程学。这反过来又往往令他们的职业生涯不那么有前途,甚至面临失业。一项研究将19世纪捷克年轻人归纳为“受过良好教育但失业”的 一群人130,类似的群体在20世纪的其他国家也有过。到了20世纪,在欧洲、亚洲和其他地方“受过教育的失业者”成为常用语。131
【注:女权分子也是如此!】
那些获得学位但没有学到在经济上有价值的技能的人会对社会失望并心生不满,成为经济中的负面因素。特别是他们会攻击那些经济上更成功的少数族群,并使得社会处理种族问题时走向极端化,成为社会的危险源。
【注:比如国产文科生~】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欧各国许多落后群体的青年刚刚接受过教育,他们发起了很多反闪米特人运动。132这些运动在政治上很得势,甚至在大学里引发了歧视甚至暴力攻击犹太学生的事件。这些来自多数人口的受挫年轻毕业生只是心生不满的人群的一部分,其中有许多人在他们家族中也是第一代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他们将自身的落后怪罪于那些更有能力的少数族群。不仅是他们,落后群体所在的知识阶层同样在推动族群身份意识和政治化。
这一趋势从东欧扩展到了世界其他地方。不论是在印度133、匈牙利134、尼日利亚135、哈萨克斯坦136、罗马尼亚137,还是斯里兰卡138、加拿大139、捷克斯洛伐克140,选修“软” 科目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会激发对成功群体的敌意,甚至暴力冲突。如今美国的许多大学和学院实行不同族群住宿分离,甚至有时对不同种族分别举办毕业典礼,以此欢呼和支持种族身份隔离,这些都会助长不公平感。141
不论是在欧洲、亚洲或其他地方,落后族群的知识分子为了留住那些可能被吸收进更大社会的个体,都会欢呼甚至捏造他们族群昔日的荣光。美国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根》 (Roots),根据此书拍摄的连续剧也很有名,历史学家曾质疑此书内容的准确性,作者的答复却是“我不过是为我的同胞创作了一个赖以生存的神话”142。
这种方式不是黑人或美国独有的。一项关于族群的国际研究发现,“族群认同的衰落”会激发起“文化复苏”143。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 曾这样说过他的爱尔兰裔美国同胞:“历史最残酷的部分是,直到1916年,美国的爱尔兰民族主义与爱尔兰基本没什么关系,它不过是一些美好感受和糟糕历史的大杂烩,美国的爱尔兰移民用它来填补他们文化的空洞。”144过分关注过去的荣光会阻碍人们接受其他文化取得的最新进展,即使这些荣光是真实的。这样的例子在中东就能看到。
不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其他时期,也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在大学中追求准确的知识与追求意识形态上的满足感是相互冲突的目标。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东中欧历史是这样描述那个年代的罗马尼亚大学的,“数据膨胀、学术上松散而政治上狂热”,已 经是“不折不扣的过剩官僚、政客和煽动者的培养皿”145。数十年后的斯里兰卡同样积压了一大批“失业毕业生”,他们的专业集中于人文社会科学。146
【注:哎,小知识分子,文科生~】
尽管一些人认为教育会提高人们对外来文化和族群的容忍度,但正是这些新近受过教育的人,由于缺失市场需要的技能而鼓动族群极端化,不论他们是在欧洲、亚洲或非洲。 正如一位著名的非洲学者观察到的:“受过教育的尼日利亚人是部落主义最糟糕的传播者。”147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19世纪的捷克知识阶层,其中包括大学生和学校老师。他们推动了捷克的文化民族主义。148他们的要求之一是布拉格的街道指示牌由原来用捷克语和德语双语,更换为只用捷克语。149在布杰约维采镇,捷克文化民族主义者要求镇管弦乐团必须演奏一定比例的捷克音乐。150
20世纪的魁北克同样在语言上坚持着一些琐碎要求。当地的法律不只要求街道指示牌用法语,而且限制私人企业使用英语。151魁北克当局甚至试图要求飞行员在飞机起飞、 降落与空中交通指挥员交流时也必须用法语。但强制使用不熟悉的语言交流,是置空乘人员的生命于危险之中。在国际飞行员威胁抵制魁北克后,当局才被迫放弃了这一要求。152
撇开种族问题,受教育年限更长也不能等同于更多的人力资本。这取决于在学校、大学和学院里待得更久是否带给受教育者更多经济上有意义的技能,或学位证书能否给获得者带来一种他能创造的东西之外的特权意识。
这并不是说教育只能产生经济方面的好处,而是说除非特定的教育和教育水准能够创 造足够多的额外产出,以此覆盖期望获得的额外收入或财富,否则认为接受教育就有权利得到更多的收入、更高的财富预期是毫无根据的。
来自落后族群、落后地区或其他落后群体的个体是他们家族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会选修挑战性不那么大的课程,因此他们的服务能够创造的价值明显不如学习有用学科,如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人。特别是在许多相对贫穷的国家,大量“受过教育的失业者”不只表达对社会的失望,甚至会成为社会和政治上的威胁。
许多拥有学位但缺乏在经济上有价值的技能的人都在政府官僚部门工作。因为竞争性市场中的雇主用的是自己的钱而不是纳税人的钱,他们对此类人没有需求。为了给大量年轻人提供工作,政府机构往往会设立一些就业岗位,否则这些年轻人会变得沮丧愤怒,让政府官员头疼,甚至给整个社会带来危险。
特别是在贫穷的国家,一些人拥有人力资本,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生产那些提升社会生活水平所需的产品。但人浮于事的官僚机构所制造的繁文缛节,经常成为他们开展经济活动的“绊脚石”。
【注:比如中国东北~】
对待工作和进步的态度
同一社会的不同群体对待工作的态度不同,不同社会之间也有不同的工作态度。这种差异显然会影响财富生产。美国南北战争前,许多人都批评南方白人缺乏职业道德。153 这些批评者不光包括北方或国外的访问者,甚至还包括罗伯特·E.李(Robert E. Lee) 将军这样忠诚的南方人。154一位知名的南方史学家说过:“许多南方白人倾向于听之任之,把变革推迟到明天。”155
【注:美国佬的地域歧视~】
德国移民先驱抵达美国的时候,他们砍伐森林以便开荒种田时,还会花费精力将树桩和树根挖走,这样就能耕种整片土地了。而南方人要么只把树砍倒,要么剥掉树皮让其自然死掉腐朽,不论何种情况,树桩都还留在地里,然后他们便围着树开垦田地。156
两个群体在乳制品生产上也形成鲜明对照。1860年,南方拥有的奶牛占全美国的40%,但生产的黄油仅占20%,奶酪仅占1%。157相对于南方地区在乳制品生产上的糟糕表现,威斯康星德国人为主的奶农则较为成功。1932年有一位学者对此的解释是:“尽职尽责,拥有稳定又有技巧的做事习惯,威斯康星的乳脂生产商早已培养出了这些品质,但这些品质还未出现在南方文化中。”158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南方白人的工作态度和做事习惯都未改变。
其他国家同样具有工作习惯上的差异。如在20世纪40年代,殖民时期的马来西亚割胶工:
许多橡胶园都会记录割胶工们每天的产出,其中华人工人和印度工人的产出差别很大。 华人工人的产出是印度工人的两倍,但他们使用的都是简单工具,如割胶刀、接胶的杯和桶。华人佃农、印度佃农以及马来佃农之间也有类似差异,甚至更大。159
一些群体逃避工作,不只是因为懒惰,还涉及更大的问题。过去,一些欧洲贵族或富人的后代从不考虑工作。但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不在此列: 欧洲大陆的贵族自矜贵族身份而不去工作,日渐贫穷。都铎时期绅士的小儿子不被允 许像他们那样在庄园无所事事,坐吃山空。他们要出去赚钱,要么从事贸易,要么从事法律工作。160
除了工作态度,对待进步的态度也会影响经济结果。在现代工业社会,人们或多或少视进步为理所应当,但进步不是必然的,即使如今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也不必然会不断进步。一位研究西方文明崛起的历史学者谈到中世纪的欧洲时说道:“当时的社会非常缺乏创新观念:人们根据习惯做事,在耕地和收割时相互配合,几代人过去了都不敢梦想去改变。”161
在这方面英国又是一个例外。英国地主很富有,但他们并不满足于被动地收地租,而是主动改进农业耕作方式。到18世纪晚期,英国成为引领农业进步的领导者之一——英国农业与东欧的封建农奴农业或西欧大陆的小农经济都有很大差异。162英国富有而有教养的阶层不仅活跃于商业、工业,也活跃于农业、文学、法律以及政治等方面。163
【注:这又是批驳海洋文明、农耕文明说的一大要点!】
相反,在20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独立国家中,新近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通常蔑视学习农业,即使农业是该国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尼日利亚就曾有超过40%的高级农业研究员岗位空缺。164直到独立后将近30年,塞内加尔才在1979年开始在大学中设置农业类学科,该国的达喀尔大学有数以千计的人文学科学生。165
在第三世界的部分地区,许多人一旦受过教育就觉得不应该从事某些手工类工作,甚至不应该去做工程师。他们“不愿意与机器打交道”166,更喜欢坐在办公室里。
这种工作态度对任何一个群体或国家都是一种文化障碍,对那些目前经济上落后的群体或国家尤其如此。有时问题不只是逃避工作或不愿意从事某种工作那么简单,而是缺乏进步的驱动力。我们再次以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南方人为例:
南方农业技术进步很慢,基本不变。犁地机这样的基本机械只在零星的地方逐渐得到应用。直到1856年,南卡罗来纳州的小户农民还在使用很原始的殖民时期的锄头。从1820 年到内战爆发,轧棉机、轧棉厂或打捆方式都没什么变化。167
南北战争爆发前南方经济的关键因素之一 ——轧棉机,是由一位北方人发明的。就一般的发明而言,1851年南方州居民获得的发明专利仅占全美国的8%,而南方白人占全美 国白人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即使在农业这一南方主要经济活动中,全美国62件专利应用 中也仅有9件出自南方人之手。168
习惯与态度上的差异,与知识和技能差异一样,也属于人力资本的差异,它们同样会造成经济结果的不同。在美国内战时期,虽然南方垄断了棉花种植,北方生产的纺织品却是南方的14倍。并且,北方生产的铁、商船总吨数和火枪分别是南方的15倍、25倍和32倍。 169
即使南方有自然资源优势,例如相对于匹兹堡或印第安纳州的盖瑞市这样的钢铁生产中心,伯明翰离铁矿和煤矿更近170,南方人力资本(劳动和管理两个方面)的匮乏却阻碍了伯明翰钢铁工业的发展。171南方林业也面临着相同的情况:自然资源丰富,人力资本匮乏。172同样,南方地区是世界领先的棉花种植区,但南方纺织工业兴起后,“许多产品还必须送到新英格兰地区进行染色、漂白、精加工等工序”173。
幸运的是,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其他地方的人涌入南方,使得该地区不断发生改变,尤其是在20世纪后半叶,变化非常明显。但不是所有的社会中的所有群体都能够发生这样的文化变迁,因为这一变化并非易事。
外来人试图改造一种文化时,通常会引发本地人的憎恨和反抗。正如知名经济史学家大卫·S.兰德斯(David S. Landes)所说的:“对文化的批判就像割开他人的自我意识, 会伤害他们的身份和自尊。”174如果没有落后群体自身对文化变迁的包容性,外来者改造一种文化的可能性很小。
注释
1David S. Landes, “Culture Makes Almost All the Difference”,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Hu man Progress, edited by Lawrence E. Harrison and Samuel P. Huntington(New York:Basic Books, 200 0), p.2.
2“Africa’s Testing Ground”, The Economist, August 23, 2014, p.59.
3比如参见Richard Lynn and Tatu Vanhanen, IQ and Global Inequality(Augusta, Georgia: Washington S ummit Publishers, 2006)。
4Victor Wolfgang von Hagen, The Germanic People in America (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6), p.326;Alfred Dolge, Pianos and Their Makers(Covina, California:Covina Publishing Compan y, 1911), pp.172, 264;Edwin M. Good, Giraffes, Black Dragons, and Other Pianos: A Technological History from Cristofori to the Modern Concert Grand(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37n;W. D. Borrie, “Australia”, The Positive Contribution by Immigrants, edited by Oscar Hand lin(Paris: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955), p.94.
5Adam Giesinger, From Catherine to Khrushchev: The Story of Russia’s Germans(Lincoln, Nebraska: 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 of Germans from Russia, 1974), pp.143—144.
6Larry V. Thompson, Book Review,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8, No. 1(May 1976), p.1 59.。同时可参见Victor Wolfgang von Hagen, The Germanic People in America, pp.242—243;Ronald C. N ewton, German Buenos Aires, 1900—1933: Social Change and Cultural Crisi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7), pp.7—8, 22。
7T. N. Dupuy, A Genius for War: The German Army and General Staff, 1807—1945(Englewood Cliffs, N ew Jersey:Prentice-Hall, Inc., 1977), p.4
8Carlo M. Cipolla, Lite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est(Baltimore:Penguin Books, 1969), pp.24, 28, 30—31, 70.
9Richard Sallet, Russian-German Settl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ranslated by Lavern J. Rippley and Armand Bauer(Fargo:North Dakota Institute for Regional Studies, 1974), p.14.
10T. Lynn Smith, Brazil: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revised edition(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 iversity Press, 1963), p.134.
11Thomas W. Merrick and Douglas H. Graham,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razil: 1800 to the Present(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11.
12Carlo M. Cipolla, Lite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p.17.
13Irina Livezeanu, Cultural Politics in Greater Romania: Regionalism, Nation Building, & Ethnic St ruggle, 1918—1930(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30, 231.
14Hain Tankler and Algo R?mmer, Tartu University and Latvia: With an Emphasis on Relations in the 1920s and 1930s(Tartu:Tartu ülikool, 2004), pp.23—24;F. W. Pick, “Tartu:The History of an E stonian University”,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5, No. 3/4(November 1946), p.159.
15Anders Henriksson, The Tsar’s Loyal Germans: The Riga German Community: Social Change and the N ationality Question, 1855—1905(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6—7;Ingeborg Fl eischhauer and Benjamin Pinkus, The Soviet Germans: Past and Present(London: C. Hurst & Company, 1986), p.16.
16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econd edi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Jack Chen, The Chinese of America(San Francisco: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0);Duvon Clough Corbitt, A Study of the Chinese in Cuba, 1847—1947(Wilmore, Kentucky:Asbury College, 197 1);Watt Stewart, Chinese Bondage in Peru: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olie in Peru, 1849—1874(D 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1951);Cecil Clementi, The Chinese in British Guiana(Georgetown, B ritish Guiana:” The Argosy” Company, Ltd., 1915);David Lowenthal, West Indian Societ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202—208.
17The Lebanese in the World: A Century of Emigration, edited by Albert Hourani and Nadim Shehadi (London:The Centre for Lebanese Studies, 1992).
18Paul Johnson, A History of the Jews(New York:Harper & Row, 1987);Jonathan I. Israel, Europea n Jewry in the Age of Mercantilism: 1550—1750(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5);Ezra Mendelsohn, The Jews of East Central Europ.between the World War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 3);Bernard Lewis, The Jews of Isla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Moses Rischi n, The Promised City: New York’s Jews, 1870—1914(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 ress, 1962);Louis Wirth, The Ghetto(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Irving Howe, World of Our Fathers(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6);Hilary L. Rubinstein, Chosen: T he Jews in Australia(Sydney:Allen & Unwin, 1987);Daniel J. Elazar and Peter Medding, Jewish Co mmunities in Frontier Societies: Argentina, Australia, and South Africa(New York:Holmes & Meier, 1983).
19Hugh Tinker, The Banyan Tree: Overseas Emigrants from India, Pakistan, and Banglades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0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econd edition, pp.277—279.
21Stanford M. Lyman, Chinese Americans(New York:Random House, 1974), Chapter 4;Betty Lee Su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1972), Chapter 3.
22Watt Stewart, Chinese Bondage in Peru, p.98. 23Duvon Clough Corbitt, A Study of the Chinese in Cuba, 1847—1947, pp.79—80;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olie Trade”, Report No. 443, 36th Congress, 1st Session, April 16, 1860, p.10.
24Duvon Clough Corbitt, A Study of the Chinese in Cuba, 1847—1947, p.80.
25Ibid.
26Stanford M. Lyman, Chinese Americans, p.152.
27Kay S. Hymowitz, “Brooklyn’s Chinese Pioneers”, City Journal, Spring 2014, pp.21, 23.
28Ibid., pp.26, 27.
29Jacob Riis,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New York: Charle s Scribner’s Sons, 1914), p.125.
30Simon Kuznets, “Immigration of Russian Jews to the United States:Background and Structure”, P 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IX(1975), pp.115—116.
31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The Children of Immigrants in Schools(Washington:Govern 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Vol. I, p.110.
32Carl C. Brigham, A Study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23), p.190.
33Charles Murray, Human Accomplishment: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800 B. C. to 1950(New York:Harper Collins, 2003), pp.291—292.
34Carl C. Brigham, “Intelligence Tests of Immigrant Groups”,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37, Issu e 2(March 1930), p.165.
35Clark S. Knowlton, “The Social and Spatial Mobility of the Syrian and Lebanese Community in Sao Paulo, Brazil”, The Lebanese in the World, edited by Albert Hourani and Nadim Shehadi, p.298.
36Luz Maria Martinez Montiel, “The Lebanese Community in Mexico:Its Meaning, Importance and the History of Its Communities”, Ibid., pp.380, 385.
37Trevor Batrouney, “The Lebanese in Australia, 1880—1989”, Ibid., p.419.
38H. Laurens van der Laan, “A Bibliography on the Lebanese in West Africa, and an Appraisal of th e Literature Consulted, “ Kroniek van Afrika, 1975/3, No. 6, p.285.
39H. L. van der Laan, The Lebanese Traders in Sierra Leone (The Hague:Mouton & Co, 1975), p.249.
40Ibid., p.236.
41Ibid., pp.237—240.
42Ibid., pp.41, 105;Albert Hourani, “Introduction”, The Lebanese in the World, edited by Albert Hourani and Nadim Shehadi, p.7 Charles Issawi,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Lebanese Emigration, 1800—1914”, Ibid., p.31;Alixa Naff, “Lebanese Immigration into the United States:1880 to the Present”, Ibid., p.145;Trevor Batrouney, “The Lebanese in Australia, 1880—1989, Ibid., p.421.
43Albert Hourani, “Introduction”, The Lebanese in the World, edited by Albert Hourani and Nadim Shehadi, p.7.
44Alixa Naff, “Lebanese Immigration into the United States:1880 to the Present”, Ibid., pp.144, 145, 147.
45Ibid., p.148.
46H. L. van der Laan, The Lebanese Traders in Sierra Leone, p.112.
47Milton & Rose 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Memoir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 8), pp.20—21. 48Alixa Naff, “Lebanese Immigration into the United States:1880 to the Present”, The Lebanese i n the World, edited by Albert Hourani and Nadim Shehadi, p.157
49Ignacio Klich, “Criollos and Arabic Speakers in Argentina:An Uneasy Pas de Deux, 1888—1914”, Ibid., p.265.
50Trevor Batrouney, “The Lebanese in Australia, 1880—1989”, Ibid., p.421.
51H. L. van der Laan, The Lebanese Traders in Sierra Leone, pp.106—109.
52David Nicholls, “Lebanese of the Antilles:Haiti, Dominican Republic, Jamaica, and Trinidad”, The Lebanese in the World, edited by Albert Hourani and Nadim Shehadi, pp.345, 351, 352, 355.
53Alixa Naff, “Lebanese Immigration into the United States:1880 to the Present”, Ibid., pp.141 —165.
54H.L. van der Laan, The Lebanese Traders in Sierra Leone, pp.210, 240, 276;Albert Hourani, “Int roduction”, The Lebanese in the World, edited by Albert Hourani and Nadim Shehadi, p.4;Clark S. Knowlton, “The Social and Spatial Mobility of the Syrian and Lebanese Community in Sao Paulo, Bra zil”, Ibid., pp.300, 304, 305;Boutros Labaki, “Lebanese Emigration During the War (1975—198 9)”, Ibid., p.625;Marwan Maaouia, “Lebanese Emigration to the Gulf and Saudi Arabia”, Ibid., p.655.
55Amy Chua and Jed Rubenfeld, The Triple Package: How Three Unlikely Traits Explain the Rise and F all of Cultural Group.in America(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 2014), p.6.
56Ibid., pp.38—39.
57Ibid., pp.39, 40.
58Andrew Tanzer, “The Bamboo Network”, Forbes, July 8, 1994, pp.138—144;“China:Seeds of Subv ersion”, The Economist, May 28, 1994, p.32.
59Robert Bartlett, The Making of Europe: Conquest, Colon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950—1350(Ne w York:The Penguin Press, 1993), pp.60, 70—84, 281, 283;Paul Robert Magocsi, Historical Atlas of Central Europ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pp.54—55;Jean W. Sedlar, East Central Europ.in the Middle Ages, 1000—1500(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4), p.116;N. J. G. Pounds,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 1800—1914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75, 449—458:Walter Nugent, Crossings: The Gr eat Transatlantic Migrations, 1870—1914(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84;Roy E. H. Mellor and E. Alistair Smith, Europe: A Geographical Survey of the Continent(New York:Colu 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92;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History, edited by Joel M oky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Vol. 2, pp.247—248.
60Glenn T. Trewartha, Japan: A Geography(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pp.78—7
61Edwin O. Reischauer, The Japanese(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62Ibid., p.8.
63Ibid., p.9.
64Tetsuro Nakaoka, “The Transfer of Cotto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from Britain to Japan”, Inte 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Europe, Japan and the USA, 1700—1914, edited by David J. Jeremy(A ldershot, Hants, England:Edward Elgar, 1991), p.184.
65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Tradition & Transformation, revised edition(Boston:Houghton-Mifflin Company, 1989), p.410.
66Irokawa Daikichi, The Culture of the Meiji Period,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arius B. Jansen(Pr 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7.
67Yasuo Wakatsuki, “Japanese E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66—1924:A Monograph”, Perspect 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XII(1979), p.431, p.434.
68Ibid., pp.414, 415.
69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revised edition, p.532.
70Ibid., p.530.
71Sydney and Olive Checkland, Industry and Ethos: Scotland 1832—1914(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 sity Press, 1989), p.147;William R. Brock, Scotus Americanus: A Survey of the Sources for Links between Scotland and Americ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 2), p.114.
72T. C. Smout, A History of the Scottish People, 1560—1830(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1 969), pp.480—489;Alexander Bain, James Mill: A Biography(London:Longmans, Green, and Co., 188 2), Chapter 1;Michael St. John Packe, The Life of John Stuart Mill(London:Secker and Warburg, 1954), p.9n.
73Henry Thomas Buckle, On Scotland and the Scotch Intellec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154.
74“The Tragedy of the Arabs”, The Economist, July 5, 2014, p.9.
75Freeman Dyson, “The Case for Blunder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6, 2014, p.6.
76Niall Ferguson,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 2011), p.47.
77Jürgen Osterhamme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lated by Patrick Camill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786.
78Toivo U. Raun, Estonia and the Estonians, second edition(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 91), pp.55, 56.
79Derek Sayer, The Coasts of Bohemia: A Czech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 8), p.77.
80Ibid., p.90.
81Paul Robert Magocsi, Historical Atlas of Central Europ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pp.37—41; Sidney Pollard, Marginal Europe: The Contribution of Marginal Lands Since the Middle Ag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53;Robert Bartlett, The Making of Europe, pp.128—132;Péter Gunst, “Agrarian System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Origins of Backwardness in Eastern Europ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from the Middle Ages Until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edited by D aniel Chiro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64.
82Anders Henriksson, The Tsar’s Loyal Germans, p.15.
83Thomas Sowell, Migrations and Cultures: A World View(New York:Basic Books, 1996), pp.181—213.
84Myron Weiner, Sons of the Soil: Migr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in India(Princeton:Princeton Uni versity Press, 1978), p.250.
85A.A. Ayoade, “Ethnic Management in the 1979 Nigerian Constitution”, Canadian Review of Studies in Nationalism, Spring 1987, p.127.
86Encyclopedia of Human Rights, edited by David P. Forsyth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 9), Volume 1, p.58.
87Cacilie Rohwedder, “Germans, Czechs Are Hobbled by History as Europ.Moves Toward United Futur 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5, 1996, p.A15.
88J. H. Elliott, Spain and Its World, 1500—1700: Selected Essay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 s, 1989), pp.225—226.
89Solomon Grayzel, A History of the Jews: From the Babylonian Exile to the End of World War II(Ph iladelphia: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7), pp.355—356, 386—393;Jonathan I. Israel, European Jewry in the Age of Mercantilism, pp.5, 6.
90W. Cunningham, Alien Immigrants to England(London:Frank Cass & Co., Ltd., 1969), Chapter 6.
91Simon Kuznets, “Immigration of Russian Jews to the United States:Background and Structure”, P 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IX(1975), p.39.
92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in Conflic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176—177.
93Hugh LeCaine Agnew, Origins of the Czech National Renascence(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 gh Press, 1993), p.51. 94Derek Sayer, The Coasts of Bohemia, p.50
95Gary B. Cohen, The Politics of Ethnic Survival: Germans in Prague, 1861—1914, second edition(W est Lafayette: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87, 91.
96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in Conflict, p.176.
97Camille Laurin, “Principles for a Language Policy”,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anadian Education: Issues and Innovations, edited by John R. Mallea and Jonathan C. Young(Ottawa:Carleton Universit y Press, 1990), pp.186, 189.
98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in Conflict, pp.176—177.
99Will Pavia, “French Zealots Just Don’t Fancy an Italian”, The Times(London), February 22, 2 013, p.28;Jeremy King, Budweisers Into Czechs and Germans: A Local History of Bohemian Politics, 1848—194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4, 128.
100例如见Stuart Buck, Acting White: The Ironic Legacy of Desegreg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1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in Conflict, p.153.
102Archie Brown, Michael Kaser, and Gerald S. Smith,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Russia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second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5.
103Ibid., pp.17—18.
104Jonathan P. Stern, “Soviet Natural Gas in the World Economy”, Soviet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World Economy, edited by Robert G. Jensen, et al(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
105Russell B. Adams, “Nickel and Platinum in the Soviet Union”, Ibid., p.536.
106Theodore Shabad, “The Soviet Potential in Natural Resources:An Overview”, Ibid., p.269.
107Nikolai Shmelev and Vladimir Popov, The Turning Point: Revitalizing the Soviet Economy(New Yor k:Doubleday, 1989), pp.128—129.
108John Stuart Mill,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ume III: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5), p.882.
109John P. McKay, Pioneers for Profit: Foreign Entrepreneurship and Russian Industrialization 1885 —1913(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p.176, 187.
110Karl Stumpp.The German-Russians: Two Centuries of Pioneering(Bonn:Edition Atlantic-Forum, 197 1), p.68.
111Alec Nove,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77), pp.100—101; Linda M. Randall, Reluctant Capitalists: Russia’s Journey Through Market Transition(New York:Ro utledge, 2001), pp.56—57.
112Raghuram G. Rajan and Luigi Zingales, 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New York:Crown B usiness, 2003), p.57.
113Bryon MacWilliams, “Reports of Bribe-Taking at Russian Universities Have Increased”, Authorit ies Say,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pril 18, 2002(online).
114Renée Rose Shield, Diamond Stories: Enduring Change on 47th Street(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94.
115Susan Wolcott, “An Examination of the Supply of Financial Credit to Entrepreneurs in Colonial India”, 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 Entrepreneurship from Ancient Mesopotamia to Modern Times, e dited by David S. Landes, et al(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458.
116S. Gordon Redd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Berlin:Walter de Gruyter, 1990), p.213.
117H. L. van der Laan, The Lebanese Traders in Sierra Leone, pp.42—43, 190, 191—192. 118“The World’s Least Honest Cities”, The Telegraph.UK, September 25, 2013.
119“Scandinavians Prove Their Honesty in European Lost-Wallet Experiment”, Deseret News, June 20, 1996;Eric Felten, “Finders Keepers?” Reader’s Digest, April 2001, pp.102—107;” The World’s Least Honest Cities”, The Telegraph.UK, September 25, 2013;” So Whom Can You Trust?” The Econo mist, June 22, 1996, p.51.
120Raymond Fisman and Edward Miguel, “Cultures of Corruption:Evidence from Diplomatic Parking Ti ckets”, Working Paper 1231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une 2006, Table 1.
121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3(Berli n: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2013).
122Nicholas Eberstadt, Russia’s Peacetime Demographic Crisis: Dimensions, Causes, Implications(S eattle: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0), p.282.
123Ibid., pp.232, 233.
124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in Conflict, p.663.
125Feroz Ahmad, “Unionist Relations with the Greek, Armenian, and Jewish Communities of the Ottom an Empire, 1908—1914”,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Empire: The Functioning of a Plural So ciety, Volume I:The Central Lands, edited by Benjamin Braude and Bernard Lewis (New York:Holmes & Meier, 1982), pp.411, 412.
126Mohamed Suffian bin Hashim, “Problems and Issues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Problems and Issues, edited by Yip Yat Hoong(S ingapore:Regional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1973), Table 8, pp.70—71.
127Sarah Gordon, Hitler, Germans and the “Jewish Ques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 s, 1984), p.13;Peter Pulzer, The Rise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 Austria, revised e dition(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0—13.
128Leon Volovici, Nationalist Ideology and Antisemitism: The Case of Romanian Intellectuals in the 1930s, 由Charles Kormos翻译(Oxford:Pergamon Press, 1991), p.60;Irina Livezeanu, Cultural Polit ics in Greater Romania, pp.63, 115;Howard M. Sachar, Diaspora: An Inquiry into the Contemporary J ewish World(New York:Harper & Row, 1985), pp.297, 299;Australian Government Commission of Inqu iry into Poverty, Welfare of Migrants(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75), p.107。
129Jason L. Riley, Please Stop Helping Us: How Liberals Make It Harder for Blacks to Succeed(New York:Encounter Books, 2014), p.49.
130Gary B. Cohen, The Politics of Ethnic Survival, p.28.
131例如见Gunnar Myrdal,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New York: Pantheon, 1968), Vol. III, p.1642;Myron Weiner and Mary Fainsod Katzenstein, India’s Preferential Policie s: Migrants, the Middle Classes, and Ethnic Equal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99。
132Leon Volovici, Nationalist Ideology and Antisemitism, 由Charles Kormos翻译, p.60。
133Mary Fainsod Katzenstein, Ethnicity and Equality: The Shiv Sena Party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in Bomba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48—49;Myron Weiner and Mary Fainsod Katz enstein, India’s Preferential Policies, pp.10—11, 44—46.
134Ezra Mendelsohn, The Jews of East Central Europ.between the World Wars, pp.98—99, 106.
135Larry Diamond, “Class, Ethnicity, and the Democratic State:Nigeria, 1950—1966”,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5, No. 3(July 1983), pp.462, 473;Donald L. Horowitz, Ethn ic Group.in Conflict, p.225.
136Anatoly M. Khazanov, “The Ethnic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Kazakhstan”,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14, No. 2(1995), pp.244, 257.
137Leon Volovici, Nationalist Ideology and Antisemitism, 由Charles Kormos翻译, passim; Josep.Roth schild, East Central Europ.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 992), p.293;Irina Livezeanu, Cultural Politics in Greater Romania, passim。
138Gunnar Myrdal, Asian Drama, Vol. I, p.348;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in Conflict, p.133; Donald L. Horowitz, The Deadly Ethnic Rio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p.1 44—145. 139Conrad Black, “Canada’s Continuing Identity Crisi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5, p.10
140例如见Gary B. Cohen, The Politics of Ethnic Survival, pp.26—28, 32, 133, 236—237;Ezra Mendel sohn, The Jews of East Central Europ.between the World Wars, p.167;Hugh LeCaine Agnew, Origins of the Czech National Renascence, passim。
141其他地方也可以见到类似的例子,如John H. Bunzel, Race Relations on Campus: Stanford Students Spe ak(Stanford:Stanford Alumni Association, 1992)。
142Philip Nobile, “Uncovering Roots”, Village Voice, February 23, 1993, p.34.还有一些批评来自Gar y B. and Elizabeth Shown Mills, “Roots’ and the New ‘Faction’:A Legitimate Tool for Clio?” T he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Vol. 89, No. 1(January 1981), pp.3—26。
143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in Conflict, p.72;以及 Keith Windschuttle, “The Fabrication of Aboriginal History”, The New Criterion, Vol. 20, No. 1(September 2001), pp.41—49。
144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Beyond the Melting Pot: The Negroes, Puerto Ricans, Jews, Italians, and Irish of New York City, second edition(Cambridge, Massachusetts:MIT Press, 1 970), p.241.
145Josep.Rothschild, East Central Europ.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p.385.
146Chandra Richard de Silva, “Sinhala-Tamil Relations and Education in Sri Lanka:The University Admissions Issue— The First Phase, 1971—1977”, From Independence to Statehood: Managing Ethnic Conflict in Five African and Asian States, edited by Robert B. Goldmann and A. Jeyaratnam Wilson (London:Frances Pinter, Ltd. 1984), p.126.
147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in Conflict, p.225.
148Robert A. Kann and Zdeněk V. David, The Peoples of the Eastern Habsburg Lands, 1526—1918(Seat 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4), p.201.
149Gary B. Cohen, The Politics of Ethnic Survival, p.148. 同时见Derek Sayer, The Coasts of Bohemia, p.101。 150Jeremy King, Budweisers Into Czechs and Germans, p.4.
151Philip Authier, “Camille Laurin, Father of Bill 101, Dies”, The Gazette(Montreal, Quebec), March 12, 1999, p.A1;Guy Dumas, “Quebec’s Language Policy:Perceptions and Realities”, Languag e and Governance, edited by Colin Williams(Cardiff: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7), pp.250—26
152Robert Bothwell, et al., Canada Since 1945: Power, Politics, and Provincialism, revised edition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9), pp.375—376;Graham Fraser, Sorry, I Don’t Speak French: Confronting the Canadian Crisis That Won’t Go Away(Toronto:McClelland & Stewart, 2006), pp.121—122.
153Grady McWhiney, Cracker Culture: Celtic Ways in the Old South(Tuscaloosa:University of Alabam a Press, 1988), pp.45—47, 49;David Hackett Fischer, Albion’s Seed: 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 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365—366, 740—743;Lewis Cecil Gray,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to 1860(Washington: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 on, 1933), Vol. I, p.484;Frederick Law Olmsted, The Cotton Kingdom: A Traveller’s Observations on Cotton and Slavery in the American Slave States(New York:Alfred A. Knopf, 1953), pp.12, 65, 147, 527;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New York:Alfred A. Knopf, 1989), Vol.I, p p.363, 369;Forrest McDonald,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South”, Geogr aphic Perspectives in History, edited by Eugene D. Genovese and Leonard Hochberg(London:Basil Bl ackwell, Ltd., 1989), pp.231—232;Lewis M. Killian, White Southerners, revised edition(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5), pp.108—109.
154Robert E. Lee, Lee’s Dispatches: Unpublished Letters of General Robert E. Lee, C.S.A. to Jeffe rson Davis and the War Department of 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1862—65, edited by Dougla s Southall Freeman, New Edition(New York:G. P. Putnam’s Sons, 1957), p.8.
155Ulrich Bonnell Phillips, The Slave Economy of the Old South: Selected Essays in Economic and So cial History, edited by Eugene D. Genovese(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07.
156Grady McWhiney, Cracker Culture, p.19;Virginia Brainard Kunz, The Germans in America(Minneapo lis:Lerner Publications Co., 1966), pp.11—12.
157Lewis Cecil Gray,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to 1860, Vol. II, p.831.
158Rupert B. Vance, Human Geography of the South: A Study in Regional Resources and Human Adequacy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2), p.168。同时见Grady McWhiney, Cracker Cu lture, p.83。
159P. T. Bauer, Reality and Rhetoric: Studies in the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4), p.7.
160G. M. Trevelyan, English Social History: A Survey of Six Centuries, Chaucer to Queen Victoria (Middlesex, England:Penguin Books, 1986), pp.140—141.
161William H. McNeill,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 Handbook, sixth edition(Chicago:Univer 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252.
162W. A. Armstrong, “The Countryside”, The Cambridge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50—1950, Vol. 1:Regions and Communities, edited by F. M. L. Thomps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 993), p.87.
163G. M. Trevelyan, English Social History, pp.243, 271—272, 315, 325, 335, 386—387, 393n, 409, 414, 419—420, 492—493.
164Carl K. Eicher, “Facing Up to Africa’s Food Crisi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66.
165Ibid., p.170.
166Gunnar Myrdal,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abridged edition(New York: Pantheon, 1972), p.296.
167Daniel J. Boorstin, The Americans, Vol. II:The National Experience(New York:Random House, 19 65), p.176.
168Grady McWhiney, Cracker Culture, p.253。1860年时,南方人口占全美总人口的39%。奴隶占南方人口的三 分之一,他们是没有办法做发明的,因此剩下的能够进行发明的南方白人占全美总人口的26%,占全部白人人口 的三分之一。相关的人口统计数据可见Lewis Cecil Gray,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to 1860, pp.656, 811。
169Paul Johnso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Harper Collins, 1998), p.462.
170Rupert B. Vance, Human Geography of the South, pp.301—303.
171Ibid., pp.304—305.
172Ibid., pp.112—116, 127—128.
173Ibid., p.292.
174Davi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New York:W. W. Norton, 1998), pp.516—517.
①20世纪初狂热的民族主义兴起后,日本的这种态度反转了。亲美时期移民美国的日本人大多在“二战”时也忠 于美国,尽管受到了战前被歧视、战争中被拘禁的对待。在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思潮兴盛时期移民巴西的日本人在 “二战”时则忠于日本,拒绝相信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美国的日侨尽管被歧视和拘禁,依然对美国忠诚;而巴 西日侨尽管比美国日侨更受优待,没有被拘禁,但他们选择忠于日本。这就再次启示我们,在界定“环境”概念 时要考虑群体的本源文化。参见Yasuo Wakatsuki,“Japanese E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66—192 4:A Monograph”,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Vol. Ⅻ(1979),pp.465—466;William Peterse n, Japanese Americans: Oppression and Success(New York:Random House,1971),pp.86—87;James La wrence Tigner,“Shindo Remmei:Japanese Nationalism in Brazil”,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 iew,November 1961,pp.51—532;Yukio Fujii and T. Lynn Smith,The Acculturation of the Japanese I mmigrants in Brazil (Gainesville: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1959),pp.49—51。
第4章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包括人口规模及其构成、人力资本和社会流动性,它们都会影响国家间和一国内部的经济差异。与地理和文化因素一样,这些社会因素在国与国之间以及一国内部并不相同。
【注:本章有批驳马尔萨斯理论的内容,因而比较重要。下面是本章内容的全部摘录。】
人 口
人口规模有时被用来解释国家间的收入与财富差异:一些国家人口过剩,因而生活穷困。除此之外,其他人口特征,如年龄、地理分布和社会流动性等也会影响个体、群体或国家的经济结果。
人口规模
几个世纪以来,不断有人担心地球上的食物无法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个体家庭、小社区到整个国家都曾有过这种担心,并且许多人担忧,人口增长将会超出地球的负担能力, 地球将无法提供足够的食物养活全世界的人口。
在那些极端贫穷的家庭,挣扎在死亡线上,甚至常常会杀死新生儿,尤其是女婴。因为他们认为女孩不够强壮,需要更长的时间成长,才能生产足够她自身生存的食物,如果她的家庭没有足够的食物养活她,她的降临会危及整个家庭的生存。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之一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不需要再面对这样绝望又痛苦的决定。
另一个益处是人类不必将大量时间精力用来种植和收获食物,因此能够将节省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发展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是文明赖以发展的基础。
更适宜的地理环境能够使人们享有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会产生更发达的文化。但这样的结果并不必然会发生。当地理环境的压力较小时,大自然能够更稳当地提供食物, 社会就会变得更不那么专注,更缺乏约束,更沉浸于酒肉和狂欢活动。地理环境的便利与施加的影响不等于地理决定论。
1798年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出版了著名的《人口论》,但在此之前人们就一直担忧地球能否提供足够的食物养活增长的人口。马尔萨斯以一种鲜明而夸张的方式提出了关于人口的理论,使这个问题成了永恒的问题。马尔萨斯的理论基于两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用马尔萨斯的话说,是“人口如果不加抑制,会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必需品“只会以算术级数增长”。第二个命题是“食物是人类生存之必需,这一自然律决定 了人口与生活必需品必须保持相同增速”1。
【注:在这方面韩非才是真正的祖师,“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 是以人民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五蠹》)】
也就是说,如果人类不控制人口增长,饥荒、疾病和其他灾难会使人口倒退到食物供给可支持的水平。自马尔萨斯的著作出版以来,这种对人口可持续性的关注时起时落,但 从未消失。2014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篇文章谈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基于“一个明显合理的前提:地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2。但是,极限的存在并不代表我们正在接近这一极限值,不论是在人口方面,还是其他方面。
“存在着人口承载极限就意味着我们正在接近这一极限”这一推论毫无道理,是典型的不合逻辑的推理。19世纪以来,无数人声称“我们正在耗尽石油、煤炭、铁矿石或其他自然资源”,但事实上他们都错了。20世纪末探明的世界石油储量是20世纪中期的10倍以上3,那时已经有人悲观地发出关于“人类正在耗竭石油资源”的警告。钢铁产量高速增长的同时,世界已知的铁矿石储量也增长了数倍。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自然资源的已知储量上。出于经济合理性考虑,不到必要的时候,即使地下有足够几个世纪使用的资源, 人们也很少愿意花钱去探寻更多的储量。4
不论马尔萨斯的理论看起来多么可信,经验证据都表明它失败了,甚至在马尔萨斯活着的时候,他的理论就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5人口规模或人口密度与人均实际收入之间 不存在完全的相关关系。撒哈拉以南非洲深陷贫困,其人口密度远远小于富裕的日本。6 可能有一些贫穷国家的人口密度高于富裕国家,但人口密度与一国的贫穷或富裕没有完全 的相关关系。时间也证明“人口过剩引致贫穷”的理论并不符合现实发展。正如20世纪一位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指出的:
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马来西亚从原来人口散布在许多小村庄和小渔村, 变成了拥有众多大城市的国家,拥有大量农业、采矿和商业活动。整个国家的人口从大约 150万增加到600万,其中马来人数量从大约100万增加到250万。相比于19世纪90年代,人口虽然多了许多,但物质生活水平更高了,人均寿命也更长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 口密集的新加坡都经历了人口的急剧增长,与此同时,人们的实际收入和工资也经历了大幅增加。今天西方世界的人口是18世纪中期的4倍多,据估计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5倍以上。 7
“人口过剩论”的鼓吹者争辩说,人口不断增加会带来贫穷,但事实上没有人可以找出这样的例子——某个国家过去的人口只有今天的一半,收入却比今天还高。
有些人认为在不同年代不同地方出现的饥荒可以支持马尔萨斯的理论。但饥荒在人口密度更高的地区如西欧和日本早已消失,却频繁地发生在人口密度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 饥荒通常是一个地区性现象,经常源于本地的谷物歉收、军事冲突或其他不利于食物分配的灾难。即使世界总体上有足够的食物,但并不是所有地区的交通系统都能够大量快速地将食物送到饥荒地区,也就无法避免大规模饥荒以及由于饥荒带来的疫病。人在饥饿状态下身体虚弱,更容易发生疾病。
随着现代运输体系的发展与扩散,饥荒越来越少了。但是,由于政治原因带来的隔绝仍会让一些地方在特定的时代遭遇饥荒。20世纪最严重的饥荒发生在30年代的苏联,造成数百万人死亡。从长期来看,这些国家都有能力提供充足的食物。8苏联时期集中发生饥荒的乌克兰,在饥荒前后都是粮食主产区之一。这些国家的人口都没有超过土地可供养的规模,甚至如今的数据显示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属于过度肥胖。9
人口结构
不同社会的人口年龄构成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在某个社会的不同种族或不同群体中也存在。日本、德国和印度人口的中位数年龄超过40岁,而危地马拉、尼日利亚和阿根廷 则不到20岁。10美国的日裔美国人比波多黎各裔美国人年龄要大20岁。11
如果成年人的工作经验从18岁算起,那么40岁工人的工作经验是20岁工人的10倍以上。这就造成了在获取知识、技能和成长的机遇上的不均等,这种不均等会造成国家间及一国 内部经济结果上的差异。
在一些国家,疾病、贫穷及其他因素会缩短人的寿命,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活到最高产的年龄段。即便是这部分人口,他们的高产期也会很短。
在一国内部,不同年龄的收入差别很大,财富差异更大。不仅如此,随着机械动力降低了人类体力的重要性,更复杂的技术又提升了知识与分析技能的价值,这些都大大降低 了年轻人所拥有的体力和精力的价值,从而增大了不同年龄组之间的收入与财富差距。这 种变化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人们获得最高收入的年龄提高了。
回到1951年,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最高值出现在35~44岁,这个年龄段的工人比20岁出头的工人多挣60%左右。到1973年,35~44岁年龄段的人收入是35岁以下年轻人的2倍多。 又过了20年,收入最高值的年龄段提高到45~54岁,他们在此年龄段挣的收入是20岁出头年轻人的3倍多。12
这些数据不足为奇,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人们在不断积累人力资本,不论是以特定知识与技能的形式,还是表现为处理人际关系或工作职责上的成熟度。我们称作“劳动”的 东西,不再是生产过程中运用体力那么简单了。许多工人提供的不仅是劳动,还包括人力资本。经济体的技术和组织越来越复杂,因而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熟练工与刚参加工作的工人之间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就是证明。
不同群体及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对孩子的抚养方式也有很大不同。一项研究发现,如果父母从事的是专业技能的职业,其子女平均每小时能听到2100个单词;如果父母是工人阶层,其子女平均每小时听到的单词量是1200个;如果父母需要接受政府福利救济,其 子女平均每小时听到的单词只有600个。13这意味着,一个成长在父母需要接受政府福利救济家庭的10岁儿童,在家里听到的单词量比父母是专业人士的家庭的3岁儿童还要少。
思考一下这种差异经年累积意味着什么,着实令人痛苦。穷人家的孩子从童年开始就面临着不利因素。这不仅限于听到的单词量,父母的素质对他们也不利。2013年的数据显示,拥有学士学位的群体中仅9%的女性是未婚生育,而未完成高中学业的群体中未婚生育的比例高达61%。14 《经济学人》杂志这样总结:“不论政府做什么,都无法让西弗吉尼亚州卡宾克里克的儿童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儿童有相同的生活境遇。”15相同的机遇意味着基于同样的标准进行评价和奖励,不可能意味着生长于差异巨大的环境中的儿童能有同等的生活机遇。
另一种说法同样表示,生活不公平与制度不公平或社会不公平是不同的。仅收集某方面的统计数据无法判断该方面就会发生不公平。如果接受社会救济家庭的子女与父母是专业人士家庭的子女属于不同的种族,那么当这些儿童长大成人,基于某个雇主的商业统计或许会显示职位高的雇员与职位低的雇员间存在的种族不平等,即便雇主在雇用和升迁中同等对待每一个人。即使这些雇员出生的时候具有相同的脑细胞,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其中一群人被认为前途光明可期,另一群人的命运却受到打击。
地理流动性
从前途糟糕的地方搬到前景更有希望的地方,这是个体与群体奋力提高经济水平的方式之一。这种迁移可以是相对短距离的,如牧羊人在一块草场的大部分牧草被吃完后转场到另一块;也可以是从一国到另一国或从一个大洲到另一个大洲,比如欧洲人移民美国或澳大利亚,印度人移民斐济群岛、马来西亚或非洲。就像其他影响人口经济水平或进步发展的因素一样,移民也不是均等的或随机的,它既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的诸多不平等, 又进一步制造了更多不平等。
对于移民,不论是在母国的移出地或者移入国的落脚处都不是随机的。一项关于“二战”前南欧人移民到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他们不是来自南欧各地,而是集中来自相对很小的一块区域”,并且“绝大多数移民定居在相邻的区域”。16从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区来到澳大利亚的意大利移民90%都定居在昆士兰州北部,而来自相邻的利帕里岛的意大利移民则大都定居于向南数百英里的悉尼和墨尔本。17
这种模式在美国甚至延伸到街区这一层面。在欧洲人大规模移居美国的时代,不论是纽约、旧金山和其他美国城市,来自意大利不同地方的移民会在不同街道聚居生活。18在同时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多伦多,来自意大利特定地区的人聚居生活也很普遍。19
这种模式在其他移民中也很常见。我们在第3章提到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黎巴嫩人开始移民到塞拉利昂,并且大多数来自黎巴嫩特定的村庄,而且在塞拉利昂选择与来自相同村庄和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比邻而居。类似地,移居哥伦比亚的黎巴嫩移民也是来自中东特定地区,在哥伦比亚也共同聚居于某个地方。20在21世纪,来自中国福建省的移民到美国时,多选择聚居在布鲁克林街区的特定地点共同打拼。21
长久以来,这种模式在全世界各地皆如此。美国肯塔基州首府法兰克福市是由来自德国法兰克福市的移民建立的。22内布拉斯加州格兰德岛最早的定居者是石勒苏益格——霍恩斯泰因人。23德国农民在18世纪移民俄罗斯,到19世纪又从俄罗斯移民美国。他们在美国既没有定居于已有的德国移民聚居区,更没有与广大美国人混居。这些来自俄罗斯的德国移民聚居于自己的社区,如伏尔加德国人和黑海德国人聚居的社区,既相互分隔开,又与其他德国人和美国人分隔开。24
这种非随机的移民聚居模式是一种规则,而非例外。倘若有人想在20世纪后半叶让纽约大都会区的北欧裔美国人和南欧裔美国人随机混杂居住,那么就需要让超过一半的南欧裔美国人搬家才能做到。25
黑人街区与白人街区的差异用肉眼就能看到,这不是因为黑人与白人的差异非常特别,只不过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差异不容易用肉眼识别。而且,在黑人街区内部,长期以来也是 不同的人群聚居在不同的地方。一项关于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黑人社区的研究发现,一些黑人街区的犯罪率超过40%,而在另外一些黑人街区还不到2%。26在哈莱姆的黑人社区, 不同居民相互分隔。其他黑人社区亦如此。27
总体而言,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都会分成不同的群体,而不同种族内部也会分成不同群体。这种同一群体内分别聚居和不同群体分别聚居的非随机居住模式是有原因的。就像人类在其他活动中表现出的模式一样,非随机定居是因为人们的行为不是随机 的,而是有目的的,不同人的目的、所处环境与价值观都是不同的。但是在许多情形下, 人们会忘记这一点,对非随机的聚居感到吃惊,还有人可能会更阴暗地看待这个结果。
社会流动性
人们在讨论中通常把社会流动性看作个人的好运。就像在19世纪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的小说中,大胆的小伙子克服逆境并最终获得正当的回报。但是,比起个人命运,社会流动性对一国的经济前途更重要。换言之,倘若一国因为种族、宗教、性别、 种姓制度或其他因素阻碍该国民众发挥才能、潜能和取得成就,就会毫无必要地剥夺使该国更加繁荣的源泉。但数千年来,这种障碍在世界各地不断涌现。
这样的障碍在有些国家更少或更弱,因而有创新性的个体和人群就会涌入这些国家,使这些国家得到快速发展。这些创新人群在原来的国家中遭受迫害,创新性被扼杀,他们 选择出逃。17世纪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由于受到宗教迫害而出走,他们造就了伦敦的制表业, 并使瑞士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制表大国。28 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犹太科学家在面临生存 威胁时逃往美国,在美国成为第一个超级核大国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29在阿根廷、 巴西、智利等拉美国家的现代工业创建过程中,移民及其后代也起了重要作用。30
同样,许多美国人白手起家,却创造甚至彻底变革了整个行业,如托马斯·爱迪生、亨利·福特、怀特兄弟、安德鲁·卡内基、大卫·沙诺夫,这些人带来的影响遍及美国甚 至全世界。因此,当有人宣称进入21世纪,美国社会流动性急剧下降时,人们对此很担忧, 经常用“社会公平”的倒退来表达这种担忧,而社会流动性的下降会影响一国的整体经济命运。
正如诸多富有感情色彩和政治影响的词汇一样,“社会流动性”和“社会公平性”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词典中把“流动”(mobile)定义为“任何可移动的物体”。显然,倘若按此定义,一辆有500匹马力引擎的汽车也是流动的,即使在某时某刻或大多数时候这辆车都停在路边。而另一辆只有250匹马力的汽车作为出租车大多数时候处在移动状态, 却不会被认为更具移动性。流动性(mobility)是事前的,移动(movement)是事后的。
类似地,我们认为流动性指的是移动的自由或选择权,而通常流动性被定义为“有多少人事实上移动了”,这两者完全不同。定义上的这些差异不仅是语言偏好那么简单,它们所谈论或暗指的内容完全不一样。
举个极端的例子,即使社会中没有阻碍个人向上流动的障碍,该社会也可能没有群体向上层流动;相反,虽然社会存在阻碍个人向上流动的障碍,特定的群体仍会克服或规避障碍向社会顶层爬升。
简言之,我们无法通过一个社会有多少人实现了向上跃升来判断社会流动性,也就是向上爬升的机会多还是少。这不只是社会给予多少机遇的问题,它同样取决于个体或群体的行动。在特定案例中事实究竟如何,这是一个实证问题,我们不能让这个问题因词汇界定上的文字游戏而化为虚无。在社会流动性这个问题上,个人选择及个体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很重要。社会并不能完全决定所有的事情,虽然有许多人不相信这一点。
如果低收入群体的本土美国人实现向上流动的比例没有低收入移民群体——如华人和古巴人——那样高,那么问题就来了:是否存在阻碍本土美国人向上流动,而移民却能豁免的外部障碍呢?这种假说可以说毫无合理性。更可信的解释可能是,低收入移民有着迥异于低收入美国人的态度与价值体系。
换言之,流动性作为机遇对于两类人是均等的,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有外部障碍或内部文化能够解释两者在流动性上的事实差异?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倘若底层美国人无法像过去那样不断向上攀升,而移民却能够不断崛起,那么就要像下一章那样,从政治因素探寻低收入美国人的境遇不断恶化的原因。
同时,我们要思考那些用经济规模扩大或缩小多少来度量社会流动性的研究。正是这类研究让人们得出结论:作为机遇的社会流动性在美国下降了。
即使我们限定讨论的框架,将流动性定义为向上流动的数量,我们仍然会面临不同的问题。例如,度量社会流动性可以通过:(1)个人一生中收入与财富增加了多少;(2) 代际间收入与财富增加了多少;(3)最新一代人的社会地位与他们父母的社会地位的差异有多大。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一系列研究发现,个体一生的收入与财富都会经历大幅提升。31户主年龄为25岁的家庭仅有13%能够挤入收入前20%,而户主年龄为60岁的家庭这一比例达73%。32这一点毫不稀奇,毕竟大多数人在职业生涯刚开始时只是挣到新人的薪水,随着时间推移,积累了工作经验、技能与成熟度,收入也随之渐涨。
把社会流动性定义为一代人相对于父母一代的收入,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幸运的是,近年来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出版了两项很有名的社会流动性研究,分别是2008年出版的《领先或节节败退:美国的经济流动性》(Getting Ahead or Losing Ground: Economic Mobility in America)和2012年出版的《追逐美国梦:代际经济流动性》(Pursuing the American Dream: Economic Mobility Across Generations)。这两项研究区分 了各种社会流动性,许多引用者却没有做到。皮尤基金会的研究有一项衡量指标是:“一 个人现在的收入、所得或财富是高于还是低于他的父母在同样年龄的所得?”33
答案是什么呢?“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家庭收入都高于他们的父母”。另外,“50%的美国人的财富高于他们父母在同样年龄时的财富”34。
另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在收入、所得或财富中的排名相对于他们父母在同样年龄时,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35换言之,子女在同代人收入序列中的位置相对于他们的父母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该研究的答案是“父母处于财富阶梯最底层的群体,其子女有66%仍处于最下两层,而父母处在财富阶梯最上层的群体,其子女有66%仍处于最上层”36。
基于这项重要发现,许多评论家认为今天美国的流动性已然变成了一个神话。但是,皮尤基金会在这两项研究中都警告过,由于缺乏历史数据,他们的研究对象并不包括移民 37,因此只能用于研究美国本土家庭。皮尤基金会在2008年的第一份研究指出,他们的研究并不适用于美国移民家庭,对后者而言,“美国梦是鲜活的且能成真的”38。这一警告非常重要。
倘若低收入移民能向上流动,而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一代又一代的相对经济地位几乎无变化,这就已经表明,美国社会仍然为人们提供经济上向上攀升的机会,只是并非所有族群都能把握住这样的机会。
智 力
关于不同种族智力的研究文献多且杂,尚未达成一致。但对于探寻当前个体或族群间经济不平等的人而言,实际的问题不是人天生的智力潜能,而是在成长中发展的人力资本, 这一人力资本伴随他们成年后工作、学习、创业或从事科学研究。
这种后天发展的能力不仅在种族或民族间差异明显,而且在生活在中心城市的人们和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山村或其他毫无希望地区的人们之间也有较大差异。这并非现代社会才出现的新现象。我们前面提到,几千年前古希腊远远领先于古代英国。在古罗马帝国时代, 西塞罗警告他的罗马同胞不要买英国奴隶,因为他们极难教化。39鉴于当时未开化的英国部落与古罗马复杂社会间有着巨大的文化鸿沟,这种情形是必然的结果。通过观察数个世纪的历史,如今我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人力资本的差距不会一成不变,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它在当时是存在的且产生影响的。
如今,虽然基因决定论的幽灵仍在游荡,但许多人不愿承认不同种族在智力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人们认为能够展示这种差异的测试“带有文化偏见”因而加以否定,而关于这种差异的历史证据又被他们当作“刻板印象”而不被认可。不同种族在雇用和晋升中的不同模式被当作“种族歧视”的证据。那些展示智力差异实证证据的人经常被扣上“种族主 义者”的标签而受到指责。有这种反应的不只是种族领袖或发言人或对种族票区负责的政治家,还有许多学者和一部分美国高等法院的法官。
这种逃避或抹黑实证证据的做法注定徒劳无功,毫无必要,不过也有一些其他的实证证据反对基因决定论。例如,来自与世隔绝的山区的美国白人,不光是个体或家庭,整个社区的平均智商接近甚至低于非洲裔美国人的平均水平。40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美国士兵进行的智力测试也显示,来自南部州的白人士兵智商低于来自北部州的黑人士兵。41尽管这样的证据削弱了基因决定论,但并不代表智力差异就没有相关性,就像在罗马帝国衰亡几个世纪后英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无法否定罗马帝国时代英国人的智力水平无法与罗马人相比一样。
预测的可靠性
通过智力测验来度量智力水平存在很大争议。但不论怎样定义真正的“智力”,都应当区分智力测验的预测可靠性与它能否度量“真正的”智力。显然目前任何智力测验都无法回溯测量“天生的智力水平”,即人在出生时的智力潜能,这正是有关先天智力的争议所在。测验的预测可靠性是又一个统计问题,我们关注的是测试结果与个人在学校、工作及其他活动中的表现的相关性。
看起来显而易见,但是在里程碑式的戈里格斯诉杜克电力公司案中,美国高等法院的裁决要求雇主“验证”哪些测验对少数族群影响不同——当这些测验“与工作能力测试无关”时。42
换言之,根据高等法院的判决,测验与工作相关的合理性是一个标准,而这种合理性是由既不懂技术又没经验的第三方来判断的,而不是基于客观的测验得分与工作表现之间 的统计相关性。倘若飞行员的IQ测验得分与空中飞行表现相关,这就表明测验的预测能力是可靠的,即使IQ测验中没有一道题是关于驾驶飞机的。不管如何定义真正的“智力”, 也不论是否能够度量天生的智力潜能,只要IQ测验的结果与飞行员接下来的表现相关,对于特定目的来说就是预测有效。
教育测验
许多测验受到批评,因为不同种族的得分往往不同,而雇用测验只是其中之一。一些对学生精挑细选的公立高中,如旧金山的洛厄尔高中或纽约的史岱文森高中、布朗克斯科 学高中以及布鲁克林工程高中,都利用这类测验决定录取哪些学生。他们也受到一些种族 群体的抨击,因为这些种族群体的学生被录取的比例很低。甚至全美国范围内的大学入学 测验也广受抨击。
就像雇用和晋升测验一样,不同族群在入学学业测验中的差异通常很大。过去,史岱文森高中入学测验中犹太学生的通过率奇高,甚至有批评者指责它是“一所免费的犹太人预科学校”或“一座拥有特权的象牙塔”。43
如今,在史岱文森高中、布朗克斯科学高中以及布鲁克林工程高中占主导的是亚裔学生。这三所学校都基于学业测验来选录学生,亚裔学生数量最多,与白人学生的比例甚至超过2 : 1。44
对高中或大学入学学业测试的批评引发的问题,核心指向教育究竟是什么以及教育在更广大的社会中起着何种作用。这些高水平学校与大学的最重要价值,并不取决于那些通过入学选拔的学生给他们自身或群体带来的益处。这些机构最重要的价值包括学生在以后的人生中通过高超的学术技能——不论是在医学、科学或其他工作中——以及他们的工作带给全社会的益处。
问题不在于这些学校有多少毕业生进入哈佛大学,也不在于布鲁克林工程高中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常年高于美国其他高中。45这些对学生精挑细选的高中作为精英学校, 真正的价值在于它们的毕业生能够比其他人给全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 史岱文森高中、布朗克斯科学高中以及布鲁克林工程高中的学生多年来赢得的各类奖项,只是它们对全社会贡献的象征。其中包括西屋科学奖、英特尔科学奖、普利策奖和众多诺贝尔奖。仅布朗克斯科学高中的毕业生,就有7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史岱文森高中和布鲁克林工程高中的毕业生,也都有人获得诺贝尔奖。
学生成为脑外科医生对于学生个体而言当然意义重大,但对那些因此被拯救的众多生命而言意义更重大。以纽约的汤森德·哈里斯高中的一名毕业生为例。乔纳斯·索尔克 (Jonas Salk)发明了一种疫苗,终结了小儿麻痹症带来的悲剧,对美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其他人取得了优秀的学业成就是人生中令人痛苦的事实。但在教育领域嫉妒优秀的人最终对社会是有害的,这不应受到鼓励。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是一小部分人力资本发展到更高水平的人取得的成就。
把斯岱文森高中指责为“一座拥有特权的象牙塔”或许显得很聪明,但聪明不是智慧。使用“特权”这个词很圆滑,如今流行把成就称作“特权”也是圆滑。这种流行扩展到教育话题之外,在其他领域也形成了有害的困惑。“特权”是事先就存在的,与事后取得的 “成就”根本不同。那些因学业成就优秀而进入高水平教育机构的学生,也完全不同于基于人口多样化或政治私利而被录取的学生。
不论纽约的这些精英公立高中招收了多少犹太学生或亚裔学生,缺乏人口多样化似乎并没有给它们的教育水准或学生未来的成就带来负面影响。而教育水准和学生的成就才是这些学校存在的意义,它们不是为了展示一幅匹配流行偏见的图景而存在的。
有些人充满激情地呼吁保障落后少数群体的利益,却很少愿意用同样的激情进行实证研究,也很少有人愿意去考察少数群体是否真正从这些呼吁中受益。纽约教育系统的其他机构实行了平等主义原则以及人口多样化,但是这不仅没有提升黑人或西班牙裔学生在这三所高中的入学测验中的通过比例,反而拉低了通过比例。46
回到1938年,进入斯岱文森高中的黑人学生占比与纽约人口中的黑人比例相当。47但自此之后,这两个比例开始变得不再匹配。20世纪后半叶,进入斯岱文森高中的黑人学生占比骤降,而这一时期黑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比1938年要高很多。到了1979年,斯岱文森高中的学生中只有12.9%是黑人。到1995年,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一比例仅为4.8%。 48到2012年,同样据《纽约时报》报道,黑人学生比例仅为1.2%。49
简言之,过去的33年间,斯岱文森高中的黑人学生录取率还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而人们常常用来解释种族差异的因素,如基因、种族歧视、贫穷或“奴隶制的遗产”,都无法解释这一倒退。回到1938年,黑人面临的种族歧视与贫穷比如今严重得多。从代际上看, 1938年的黑人也更接近奴隶制。很显然,其中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这种令人心痛又困惑的变化趋势,对那些遗传决定论或环境决定论者是一种挑战。这里的“环境”是指通常的社会经济学定义的环境。更早时候的黑人学生为什么更容易通过高标准的智力测验,进入精英公立高中?对于这一问题,找不到明显可信的基因解释。然而,使用社会经济定义的“环境”来解释更让人困惑,因为1938年以后,黑人的社会经济条件,不论是绝对意义上还是相对于总体而言,都有很明显的改善。除此之外,仅有的可能性是,这些年来黑人社区文化在某些方面变得更糟了。
黑人内部有不同的文化。其中一种是古老的南方文化,它也给南方白人带来了众多障碍。50表现之一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方州的白人士兵智力测验成绩很低。51
美国内战后,数以千计的北方志愿者来到南方,他们肩负的使命是教育被解放奴隶的子女。他们的领导者在行动中,假定教育的主要目标是用新的文化代替黑人中的南方文化。 这一前提得到公开宣扬52,这一点与我们如今的情况完全相反。我们今天认为,在教育中保留和赞美黑人文化很重要。
美国内战后,来自北方的教育者相当大比例来自新英格兰地区。他们努力用完全不同的新英格兰文化取代黑人的南方文化。由于经济资源有限,这仅仅在少数教育机构实行了。 但就是这样的少数教育机构培养了与它们自身数量不成比例的众多领域的黑人领袖和先驱。 53
其中一个机构是1870年华盛顿特区创立的全美第一所黑人公立高中。1899年,该市的四所学术型高中(三所是白人学校,一所是黑人学校)进行了测验,该黑人学校的成绩高于三所白人学校中的两所。54
这一成功并非侥幸。尽管非洲裔美国人IQ平均值一直徘徊在85左右,这所黑人学校(名字不时有变动,1916年以后叫邓巴高中)学生的IQ值在1938年至1955年间——除了1945年是99分——从未低于100分。55该校入学时没有进行IQ测验,许多学生的IQ低于100, 但由于他们的学业成绩很强也被录取了。56这所学校同样也没有“种族多样性”。1870年至1955年间,该校学术上处于优势地位,并且在长达85年的时间里学生全都是黑人。
在那个年代,该校的大多数毕业生都能进入大学深造,不论是黑人高中生还是白人高中生,当时都很罕见。19世纪末,该校的毕业生陆续进入精英大学深造,1903年该校有了第一名被哈佛大学录取的毕业生。1892年至1954年间,艾姆赫斯特学院录取了34名该校毕业生,其中74%顺利毕业,28%获得全美大学优等毕业生荣誉。57不只是艾姆赫斯特学院, 该校毕业生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艾姆赫斯特学院、威廉姆斯学院、康奈尔大学、达 特茅斯学院等老牌大学后,都曾获得过全美大学优等毕业生荣誉。58
该校的第一批毕业生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成为进入许多领域的首个黑人。包括安那波利斯市的第一名黑人毕业生59,第一名应征入伍当上军官的黑人士兵60,第一名从美国大 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黑人女性61,第一名黑人联邦法官,第一名黑人将军,第一名黑人内阁 成员。还有许多其他名人,如凭借在血浆应用上的开创性工作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查尔斯·德鲁(Charles Drew)博士。62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中的黑人军官还很少, 邓巴高中有许多毕业生成为军官,包括“上尉和中尉、大约20名少校、9名上校和中校以 及1名准将”63。
所有这些名人都来自同一所黑人社区的公立高中,这着实了不起。其中就有相关的文化因素在起作用,这所学校自创始起就拥有完全不同于贫民区的文化。前10位校长中有7 位在新英格兰环境中接受教育,有4位从建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大学获得学位,有3位从欧柏林大学获得学位。欧柏林大学是一所由新英格兰人在俄亥俄州建立的大学,目的是将新英格兰文化移植到中西部。邓巴高中给每个学生分发行为手册,对学生在校内外应当如何言行讲得很清楚。64而如今给这些学生教授这类价值观和行为举止会被批评者认为“举止模仿白人”。
当地黑人社区对邓巴高中学生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也没有视而不见。实际上,在华盛顿黑人中,邓巴高中引发了很大争议,以致后来的普利策奖获得者、《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专栏作家威廉姆·拉斯贝瑞(William Raspberry)说,只要提到“邓巴” 这个词,你就可以将这个城市里的中年黑人的任何社交联谊会变成不同派系间的冲突。65 在华盛顿黑人社区,对邓巴高中的怨恨就像对纽约老牌公立高中的怨恨或世界其他国家对成功者的怨恨一样。
当更现代的教学楼建成后,对于如何处置将被代替的邓巴高中旧建筑引发了争议。骄傲的校友与反对邓巴高中的黑人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演变成了联邦案件,提交给美国巡回上诉法庭来裁决。在华盛顿市议会提出该议题时,一位议员说:“本市有些人说这所高中代表了黑人中的精英主义,这种精英主义不应该再次发生。让我说,我们应该把它夷为平地。”66校友一方在法庭诉讼中败诉,邓巴高中的旧建筑被拆除。20世纪后半叶, 贫民区文化在全美国各地取得了大量胜利,邓巴高中只是其中一例,而由此带来的影响扩展到了教育机构之外。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社会氛围变了,其中包含对贫民区文化的颂扬,其实质是美国南方错乱的农人文化的一个分支。67这种文化却经常被当作黑人甚至非洲人独有的东西, 即使证据表明恰恰相反。①这一贫民区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甚至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黑人年轻人也觉得有必要接受贫民区文化,包括其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以显示种族团结,避免被冠以“举止模仿白人”的污名。否则在社交活动中,他们就可能遭受嘲笑、排斥甚至威胁和直接的暴力攻击。
传奇的篮球球星卡里姆·阿卜杜·贾巴尔(Kareem Abdul-Jabbar)描述了作为一名年轻人在这样的文化中成长究竟如何:
我所有的成绩都是A,也因此别人讨厌我;我发音标准,别人就叫我“朋克”。为了应对这些威胁,我不得不学会一种新的语言。我举止得体,是个好小伙子,但不得不隐藏自我。68
这不是某时某地发生的单个事件,这种文化在全非洲裔美国人中的影响力不断增长。
在俄亥俄州榭柯高地的富人郊区,各种族杂居,然而对当地黑人年轻人的一项研究发现, 这些年轻人在学业上远远落后于同年龄段的白人。这背后的原因很容易探寻:黑人学生用 在学习上的时间太少了,看电视和其他活动占据了他们太多时间。69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懒 惰问题。当地黑人中存在着事实上的厌恶那些“举止模仿白人”的行为。根据对这些黑人 学生的调查,研究者认为,“最受批评的‘白人言行’是‘谈吐得体’”70。换句话说, 讲标准英语被当作种族背叛。
这位研究者说:“最让我震惊的是,这些来自医生和律师家庭的小孩,思考方式不像他们的父母。他们不知道父母是如何成功的。”相反,他们“把贫民区的说唱歌手当作模仿的偶像,他们学的都是娱乐明星”。71年轻人面临的正常激励大大减少了,因为不论学生是否学到了应该学到的知识,学校都会让学生升级。这样一来,年轻人会因短视而把教育丢在一旁,也就丢掉了未来过上更好生活的机会。当被问到为什么不认真对待学习时, 榭柯高地的许多黑人学生说,不论成绩及不及格,都不会留级。72毕业以后的生活显然不在他们的视野里。
还有很多成年人,降低了黑人年轻人认真对待学校功课的激励,其中不只有学校教师和管理者,还包括许多黑人领袖和发言人。后者就像其他国家落后种族的领袖和发言人一 样,将他们族群的问题归咎于他人,把反对其他族群及其他文化描述为前进的途径。除此之外,许多知识界和教育机构的人士本着帮助黑人的精神,也赞同他们的主张。马丁·路 德·金是抵制这种做法的黑人领袖之一,他说:“我们不能总是责备白人,为了我们自己, 有些事必须我们自己去做。”73但这种观点并没有压倒前面提到的观点。
不只老牌学校中的黑人年轻人的教育在退步,贫民区学校更是被其他学校甩在后面,这如今也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但是这种情况并非一直如此。有人可能会感到吃惊,1941 年的时候,纽约黑人社区哈勒姆区小学各班的测验成绩与同年级纽约下东区工人阶层社区 的白人学校差不多。
1941年4月,哈勒姆区小学6年级的学生在某些问题上答得更好,在另一些问题上则是下东区白人学校学生答得更好。1947年5月,这两个区的3年级学生情况也是如此。1941年12月的时候,哈勒姆区小学6年级学生回答问题都好于下东区白人学校的6年级学生。而到了1951年2月,下东区初中学生的成绩要好于黑人社区的一所男校和一所女校的平均成绩。 74
简言之,从样本的情况来看,黑人社区学校和下东区学校的测验成绩没有极大的差别。 这些都是普通工人阶层社区的学校,不论是白人学校还是黑人学校,在教育结果上不存在真正的差异。
此后黑人社区的文化逐渐退步。比起遗传理论和环境理论(环境通常被定义为周遭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区别于文化价值的内在变化),这种文化上的退步更能解释为何黑人教育倒退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在同一时期,黑人社区的社会退步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黑人儿童由双亲家庭抚养长大转变为绝大多数由单亲家庭抚养。
还要指出的是,尽管在许多黑人社区贫穷司空见惯,但1994年以后,黑人已婚夫妇的贫穷率下降到了个位数。75换言之,那些避开了贫民区文化泛滥的黑人比其他黑人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了贫穷。
文化很重要。贫民区文化并不是新东西。但直到20世纪后半叶,这种文化还仅仅局限在贫民区,没有扩散到其他黑人社区。后来这种文化却受到黑人知识阶层和白人知识阶层的推崇。
学院与大学
平权主义与人口“多样性”标准在大学中也取得了胜利,甚至连精英大学的录取政策和在实际录取中也实行这一标准。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标准究竟对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在 大学及职业生涯中的表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平权政策能确保校园里有更多的少数群体学 生,但无法保证他们能顺利毕业,更不要提从很有挑战性的数学、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毕业。
虽然20世纪8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的黑人学生数量增加了,但是毕业的黑人学生数量却减少了。76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加州大学取消了录取上的平权措施,于是加州大学录取的黑人学生数量略有下降,但毕业的黑人学生却增加了。西班牙裔学生的毕业人数也增加了许多。77这是因为加州大学各校区录取的少数族裔学生,不再仅仅是因为人口多样性,这些学生能够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或洛杉矶分校录取,是因为他们的学业符合入学条件。
取消平权措施之后,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成功毕业的人数在接下来的四年间增加了55%;并且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毕业生数量增加了51%;毕业学分绩点不低于3.5的毕业生数量则提高了63%。这些结果都证实了学术界长久以来对平权运动的批评:那些不符合这些教育机构录取标准的学生,有的无法顺利毕业,有的虽然毕业了,学习的却是相对容易的专业,而不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
由前大学校长威廉·鲍恩(William Bowen)和德雷克·博克(Derek Bok)合写的 《河流之形》(The Shape of the River)一书认为,平权运动是成功的。该书广受称赞, 但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缺陷:
1.该研究的目标是揭示平权运动政策下,学业资格不够但被录取的黑人学生表现得很好。但是,该研究的样本是所有的学生,包括与其他学生具有相同入学条件的黑人学生和因为平权政策而被录取的差一些的黑人学生。78统计数据中缺乏与问题对应的那些条件差一些但仍被录取的黑人学生群体的数据,就像《哈姆雷特》中没有丹麦王子一样。
2.鲍恩和博克发现,在他们的样本中,“学校对学生的选择越严格,黑人学生毕业率越高”79,看起来这是一种胜利,但这并非对错配假说的检验。错配假说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学校,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的入学资格条件差异越大,两个种族未能毕业的比例差异也应该越大。要验证错配假说,就要选定具体的某个机构[特恩斯特伦(Thernstrom)著的 《黑人和白人的美国》(America in Black and White)就是这样做的],而不是将不同 SAT水平的学校混在一起进行验证。这两项研究都使用了组合SAT成绩来衡量学业水平。 《黑人和白人的美国》一书的数据表明,哈佛大学的黑人学生和其他学生的组合SAT成绩 相差95分(分别是1305分和1400分),莱斯大学的黑人学生和其他学生的组合SAT成绩分 差为271分。相应的退学率,哈佛大学的黑人学生比白人学生高2个百分点,而莱斯大学两者的退学率相差15个百分点。80在鲍恩和博克的研究中,莱斯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处于一个集合中81,实际上普林斯顿大学不同种族学生的SAT成绩差别远小于莱斯大学,相应的退学率差别也小,仅为4个百分点。并且他们的研究在筛选高SAT成绩学校时完全忽略了哈佛大学。当他们聚焦于不同集合的比较时,眼里就没有“用同类学校来证实错配假说”。 用加总法能获得统计上令人惊叹的结果,但用个体学校来检验时,这些结论就不一定站得住脚了。其他对个体学校研究的数据得到的结果也与《黑人和白人的美国》很相似,却与 《河流之形》的结果相差很大。82
3.鲍恩和博克所使用的原始数据,其他研究者无法获得。83
鲍恩和博克的著作获得的称赞甚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结论在许多地方广受欢迎,与他们在书中呈现的证据或逻辑的质量无关。他们的结论恰好符合流行的观念,这就足以使他们豁免而不必遵循结论与事实相符的要求了。
天生的潜力
**后天开发的智力与天生的智力潜能相比不仅更容易测量,而且显然更重要。事实的确如此,天生潜力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它是后天开发智力的源泉或极限。不论雇一个水管工或是找一个外科医生看病,我们最想知道的是他们在水管工程或手术上的技能,而不是这 一技能来自遗传还是环境。 **
20世纪初,基因决定论盛行,提倡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假定遗传潜能决定了某些种族在智力发展上的“天花板”,认为群体中某些成员的智力水平决定了他们注定只能做“劈柴挑水”的工作,因此基因决定论者支持优生学,该术语引自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他主张让“劣等民族逐步灭绝”84。
优生运动跨越了大西洋。更引人注目的是,赞成这一优生运动的群体涵盖了整个意识形态“谱系”,在英格兰包括从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尼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这样的保守派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 es)这样的左派,再到费边社会主义的领导者,而在美国也同样席卷了从杰克·伦敦(Ja ck London)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到保守主义偶像亨利·L.门肯(Henry L. Mencken)。
在那个年代,美国基因决定论者的许多论著展示给大家的,是东欧人和南欧人先天在智力水平上低于北欧人。当时从欧洲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已由最初的主要来自北欧地区转 变为主要来自东欧和南欧,这就引发了对智力较低文化上又无法同化的移民涌入美国的恐慌。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黑人天生劣等,这一观念深入人心,反而没有大量的研究文献。 85
在基因决定论的影响力达到顶点时,出现了不支持这些结论的实证证据。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以犹太人为例,其智商测验成绩高于全美国平均水平86,连智商测验先驱卡 尔·布里格姆都放弃了其原先的观点。87还有人提到,军队智商测验中一些南方州的白人士兵成绩不及一些北方州的黑人士兵高。88这也使得最广为接受的“基因决定论”的种族版本“坍塌”了。
这样的结果不仅不支持基于基因决定论的黑人——白人智商测验差异,而且与北欧人天生智力优于南欧人的假设也不一致,因为定居在美国南部的白人主要是来自英国等假设 中更优等的北欧人,而来自东欧和南欧的大规模移民主要定居于北方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者对黑人士兵智商测验成绩的深入考察,引发了对黑人文化水平的探讨。正如卡尔·布里格姆在重新检视自己的研究结论——关于非英语家庭长大的白人移民时,也引发了文化相关的问题。
当时接受军队智商测验的黑人的识字率很低,这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尽管很少有评论者将其纳入讨论。参加军队智商测验的黑人士兵的低识字率会影响测试结果:他们能够更多地回答那些难度更大但无须理解书面意思的题目,却不太容易回答那些难度不大但需要理解书面意思的题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阿尔法测验的多个部分,黑人士兵的中位数得分是0。测验的问题包括“是”和“否”是一对反义词、“黑夜”和“白天”是一对反义词、“苦” 和“甜”是一对反义词等诸如此类非常简单的问题,任何懂得“反义词”含义的人都不会答错。考虑到黑人识字率低这样的事实,我们就能理解黑人的测验结果了。 对不识字的士兵进行军队贝塔测验,问题包括看一堆积木的图片,判断有多少个积木, 有些积木直接看不到,但依据积木堆积的形状可以进行推断。这些不识字的黑人士兵在此类题目上得到0分的比例低于一半。这些题目在智力上更有挑战性,但不要求理解“反义词”这样的字眼。当时,在差一些的南方学校,许多黑人所受教育可以忽略不计。
鉴于那一代黑人接受的教育少得可怜又很差,即使从技术上看,识字的黑人也不太可能有很大的词汇量。完全不识字的黑人在更有挑战性的题目上的表现比有一定阅读能力的黑人在更简单题目上的表现更佳,这也就不难理解了。89
数十年后,移居新西兰的美国教授詹姆斯·R. 弗林(James R. Flynn)的一项研究指出,IQ测验的原始成绩会在一到两代人内提高一个标准差甚至更多,并且这种现象已经发生在十几个国家中。90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IQ测验的成绩度量了不变的基因禀赋”这一观念了。
随着测验的正确率不断变化,为确保IQ平均值保持在100,IQ测验的标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掩盖了IQ原始成绩大幅提高的事实。其中包括非洲裔美国人的原始成绩,尽管标准改变后他们的成绩只维持在85分。用1947—1948年的标准来衡量,2002年非洲裔美国人平均答对的题目得分为104分,也就是说,略好于1947—1948年全美平均分。91
IQ差距是否或多大程度上源于遗传,这是有待回答的问题。即使是某些方面如身高,大家都同意主要由遗传决定,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身高差都是遗传决定的,更不是说在某些情形下,遗传之外的其他因素不会造成身高的变化。
例如,从18世纪初到20世纪,英国人的平均身高曾经高于法国人,1967年以后两国的平均身高持平。92从19世纪中期到21世纪初,荷兰年轻男性的平均身高从1.62米增高到了 1.82米。93
20世纪初流行的基因决定论不过是将人类一千年历史中的一小段推而广之得出的,因此即使没有这些实证发现,它也会受到质疑。当时在讨论美国移民法案时经常被提及的主题就有:来自南欧的移民在教育和其他方面不如北欧人,并且这种劣等是天生的、遗传的, 而且是持久的。94
过去数百年里,北欧国家确实在经济、科技等许多方面都超过了南欧,但在古代南欧却远远领先于北欧。没有迹象表明两地人的基因发生了变化。同时,经过几百年,曾经领先于所有欧洲国家和日本的中国落后了,日本赶超了中国,这些地方的人的基因同样都不曾有过变化。
换个方式看,我们会发现相似的地理环境会产生非常相似的经济与社会模式,即使这些不同地区的人种族不同,也毫无基因上的联系,比如世界各地不同地区的山地社区。基因决定论者必须解释不同群体间的这种非基因决定的偶然相似性,他们还必须解释,落后的群体,如加那利群岛的岛民、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地以及澳大利亚土著,为什么会长期与世隔绝。
有许多白人的IQ得分与非洲裔美国人一样,甚至更低。美国人平均IQ得分包含了不同种族以及不同个体间差异巨大的得分,所以将各个群体的平均值与全美国平均值比较都非常独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欧洲向美国大移民的时代,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希腊、 葡萄牙和波兰的移民的IQ得分并不比非洲裔美国人高。95其他还有一些白人族群的平均IQ得分也不比非洲裔美国人高,包括美国山区白人、英国运河船民、苏格兰赫布里特群岛讲盖尔语的白人。96
简言之,基因决定论者想要用基因来解释不同种族取得的成就背后蕴含的社会模式,既不必要也不充分。不论基因在医学或其他科学中有多重要,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对于不同种族的智力究竟有何影响仍是有待求解的问题。
即使我们接受IQ测验是普遍适用的智力测验,黑人的IQ得分上限也高于白人的IQ平均得分,尽管整体上前者的IQ得分低于后者。20世纪初的基因决定论者提倡的优生议程有一项隐含的假定,即特定种群的智商水平存在“天花板”,而不是单纯的智力平均水平在某时某地更低。
即使在智力潜能差不多的族群中,不同群体因环境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生育率和生存率,最终造成智力平均值的差别。换言之,即使IQ的上下限没有变化,环境也能改变IQ的统计平均值。例如,有人提出,未能重新审视 “当今的福利政策”助推了黑人社区低收入家庭更高的生育率,这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在对待黑人上最大的不平等。那些无法通过军队智商测验的黑人,有四分之三来自有四个或四个以上小孩的家庭。97
不论哪个种族,父母是专业人士的家庭,儿女数极少会超过3个。但对于高中辍学的未婚少女妈妈,生育3个以上孩子很普遍。一旦她们挥霍了教育机会,在一个没有好机会的世界中,孩子就成了他们的“餐票”。美国政府的政策人为地提高了母亲是未婚辍学黑人少女的比例,这对于黑人群体或全社会都无益处。
对基因决定论的抵制在此之后产生了一种社会哲学,这种哲学与基因决定论一样缺乏证据支撑。今天的文化多元主义者拒绝承认“一些人在某时某地的成就优于或不如他人”。 尽管古代希腊人很明显领先于英国人,而到了19世纪,英国人领先希腊人。今天一些测验表明,在某些事情上,一些群体远远优于其他群体,但这些测验结果被当作有偏误而不被理会。显然根据此种观点,在给定的时间或地点,一些群体优于或逊于其他群体是不可能 的,即便可能,我们也不能公开承认。
这种对基因决定论的反应或过度反应对于落后群体尤其有害,因为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和精力从许多能提升自我和让他们前途更光明的方法上转移开了,反而将他们引入了憎恨和抨击他人的死胡同。实际上,历史上有许多落后群体是通过提升自己摆脱了落后境地, 实现赶超。
注释
1Thomas Robert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London:J. Johnson, 1798), p.14; Thomas Robert Malthus, Population: The First Essa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 9), p.5;Thomas Robert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 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with Remarks on the Speculations of Mr. Godwin, M. Condorcet and Other W riters”, On Population, edited by Gertrude Himmelfarb(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1960), p.9.
2Eduardo Porter, “Old Forecast of Famine May Yet Come True”, New York Times, April 2, 2014, p.B1.
3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Basic Petroleum Data Book, Volume XX, No. 2(Washington:American P etroleum Institute, 2000), Section II, Table 1.
4见我的另一本书Basic Economics: A Common Sense Guide to the Economy, fifth edition(New York:Basi c Books, 2014), pp.294—301。
5见我的另一本书On Classical Economic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57—63, 120—1 22。
6Geography of Sub-Saharan Africa, third edition, edited by Samuel Aryeetey Attoh(New York:Prenti ce Hall, 2010), p.182;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2013(New York:World Almanac Books, 2013), p.793.
7P. T. Bauer, Equality, the Third World and Economic Delusion(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 niversity Press, 1981), p.43.
8Paul Robert Magosci, A History of Ukraine(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p.6; Norman Davies, Europ.at War, 1939—1945: No Simple Victory(London:Macmillan, 2006), p.32;Tony Judt,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Since 1945(New York:Penguin Books, 2006), p.648. 9Shirley S. Wang, “Obesity in China Becoming More Common”,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8, 2008, p. A18.
10The Economist, Pocket World in Figures:2014 edition(London:Profile Books, 2013), p.18.
11
族群/群体 中位数年龄
黑人 32.9
柬埔寨裔 31.0
华裔 38.0
古巴裔 39.8
日裔 49.5
墨西哥裔 26
波多黎各裔 28.4
白人 40.2
总人口 37.4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调查局2012年美国社区调查。
12W. Michael Cox and Richard Alm, “By Our Own Bootstraps:Economic Opportunity & the Dynamic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nual Report 1995,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p.16.
13“Choose Your Parents Wisely”, The Economist, July 26, 2014, p.22.
14Ibid.
15Ibid.
16Charles A. Price, Southern Europeans in Australia(Melbour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276;Charles A. Price, The Methods and Statistics of ‘Southern Europeans in Australia’(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63), p.21.
17Charles A. Price, Southern Europeans in Australia, p.162.
18Philip Taylor, The Distant Magnet: European Emigration to the USA(New York:Harper & Row, 197 1), pp.210, 211;Jonathan Gill, Harlem: The Four Hundred Year History from Dutch Village to Capit al of Black America(New York:Grove Press, 2011), p.139;Robert F. Foerster, The Italian Emigrat ion of Our Times(New York:Arno Press, 1969), p.393;Dino Cinel, From Italy to San Francisco: Th e Immigrant Experien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28.
19Samuel L. Baily, “The Adjustment of Italian Immigrants in Buenos Aires and New York, 1870—191 4”,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April 1983, p.291;John E. Zucchi, Italians in Toronto: Developme nt of a National Identity, 1875—1935(Kingston, Ontario: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41, 53—55, 58.
20Louise L’Estrange Fawcett, “Lebanese, Palestinians and Syrians in Colombia”, The Lebanese in the World: A Century of Emigration, edited by Albert Hourani and Nadim Shehadi(London:The Centre for Lebanese Studies, 1992), p.368.
21Kay S. Hymowitz, “Brooklyn’s Chinese Pioneers”, City Journal, Spring 2014, pp.20—29.
22Theodore Huebener, The Germans in America(Philadelphia:Chilton Company, 1962), p.84.
23Hildegard Binder Johnson, “The Location of German Immigrants in the Middle West”, Annals of th 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edited by Henry Madison Kendall, Volume XLI(1951), pp.24 —25.
24LaVern J. Rippley, “Germans from Russia”,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edit ed by Stephan Thernstrom, et al(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427.
25Edward C. Banfield, The Unheavenly City Revisited(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4), p.
26E. Franklin Frazier, “The Impact of Urban Civilization Upon Negro Family Life”, American Socio logical Review, Vol. 2, No. 5(October 1937), p.615.
27Jonathan Gill, Harlem, p.284;E. Franklin Frazier, The Negro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ised editi on(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7), pp.239, 257—258;Willard B. Gatewood, Aristocrats of Color: The Black Elite, 1880—1920(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94—195;St ephen Birmingham, Certain People: America’s Black Elite(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 7), pp.196—197;” Sugar Hill:All Harlem Looks Up to ‘Folks on the Hill’”, Ebony, November 1 946, pp.5—11.
28Carlo M. Cipolla, Clocks and Culture: 1300—1700(New York:Walker and Company, 1967), pp.66—6
29在推动罗斯福总统发起曼哈顿计划和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犹太科学家所起的作用可见Richard Rhodes, 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New York:Simon & Schuster, 1986), pp.305—314。 As for the scientists being Jewish and playing major roles in that project, 见同书,pp.13, 106, 188—189;Silvan S. Schw eber, Einstein and Oppenheimer: The Meaning of Genius(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 y Press, 2008), p.138;Michio Kaku, Einstein’s Cosmos: How Albert Einstein’s Vision Transformed Our Understanding of Space and Time(New York:W. W. Norton, 2004), pp.187—188;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America(New York:Alfred A. Knopf, 1992), p.527;American Jewish Histor ical Society, American Jewish Desk Reference(New York:Random House, 1999), p.591。
30Fernand Braudel,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translated by Richard Mayne(New York:Penguin Book s, 1993), p.440.
31W. Michael Cox and Richard Alm, “By Our Own Bootstraps:Economic Opportunity & the Dynamic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nual Report 1995,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p.8;” Movin’ On Up”,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3, 2007, p.A24。加拿大也存在类似的模式 , 见Niels Veldhuis, et al., “The‘Poor’Are Getting Richer”, Fraser Forum, January/February 2013, pp.24, 25。
32Thomas A. Hirschl and Mark R. Rank, “The Social Dynamics of Economic Polarization:Exploring th e Life Course Probabilities of Top-Level Income Attain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4 Annual M eetings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Boston May 1–4, 2014, p.13.
33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Pursuing the American Dream: Economic Mobility Across Generations(Wa shington: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 an initiative of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2012), p.1。在皮 尤基金会2008和2012年的研究中,这项指标被称为“绝对流动性”; Isabel V. Sawhill,“Overview”, Julia B. Isaacs, Isabel V. Sawhill and Ron Haskins, Getting Ahead or Losing Ground: Economic Mobility in America(Washington: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 an initiative of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2008), p.2。
34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Pursuing the American Dream, p.2.
35Ibid., p.1.在这两项研究中, 这项指标均被称为“相对流动性” ;Isabel V. Sawhill, “Overview”, Jul ia B. Isaacs, Isabel V. Sawhill and Ron Haskins, Getting Ahead or Losing Ground, p.2。
36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Pursuing the American Dream, p.2.
37Ibid., p.28. A similar caveat appears in the 2008 study on page 105.
38Isabel V. Sawhill, “Overview”, Julia B. Isaacs, Isabel V. Sawhill and Ron Haskins, Getting Ahe ad or Losing Ground, p.6.
39Eligio R. Padilla and Gail E. Wyatt, “The Effects of Intelligence and Achievement Testing on Mi nority Group Children”, The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Group Children, edited by Gloria Johnson Powell, et al(New York:Brunner/Mazel, Publishers, 1983), p.418.
40Mandel Sherman and Cora B. Key, “The Intelligence of Isolated Mountain Children”, Child Develo pment, Vol. 3, No. 4(December 1932), p.283;Lester R. Wheele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nte lligence of East Tennessee Mountain Childre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Vol. XXXIII, No. 5(May 1942), pp.322, 324.
41Otto Klineberg, Race Differences(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1935), p.182.
42Griggs et al. v. Duke Power Co., 401 U.S. 424(1971), at 432.
43Heather Mac Donald, “How Gotham’s Elite High Schools Escaped the Leveller’s Ax”, City Journa l, Spring 1999, p.74.
44Jason L. Riley, Please Stop Helping Us: How Liberals Make It Harder for Blacks to Succeed(New Y ork:Encounter Books, 2014), p.49.
45Susan Jacoby, “Elite School Battle”, Washington Post, May 28, 1972, p.B4.
46Dennis Saffran, “The Plot Against Merit”, City Journal, Summer 2014, pp.81—82.
47Reginald G. Damerell, Education’s Smoking Gun: How Teachers Colleges Have Destroyed Education i n America(New York:Freundlich Books, 1985), p.164. 48Maria Newman, “Cortines Has Plan to Coach Minorities into Top Schools”, New York Times, March 18, 1995, p.1.
49Fernanda Santos, “Black at Stu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6, 2012, Metropolitan Desk, p.6.
50见我的另一本书Black Rednecks and White Liberals(San Francisco:Encounter Books, 2005), 以及Cra cker Culture: Celtic Ways in the Old South(Tuscaloosa: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8)by Grad y McWhiney and Albion’s Seed: 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by David Hackett Fischer。
51H.J. Butcher, Human Intelligence: Its Nature and Assessment(New York:Harper & Row, 1968), p.2
52President Wm. W. Patton, “Change of Environment”, The American Missionary, Vol. XXXVI, No. 8 (August 1882), p.229;James D. Anderson, The Education of Blacks in the South, 1860—1935(Chape 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p.46.
53见我的另一本书Black Rednecks and White Liberals, pp.38—40。
54Henry S. Robinson, “The M Street High School, 1891—1916”, Records of the Columbia Historical Society, Washington, D. C., Vol. 51(1984), p.122.
55见我的文章 “Assumptions versus History in Ethnic Education”,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Volume 8 3, No. 1(Fall 1981), p.47, 表4 , 学校代码0508/0598。
56Mary Gibson Hundley, The Dunbar Story: 1870—1955(New York:Vantage Press, 1965), p.25.
57Ibid., p.75.
58Ibid., p.78. Mary Church Terrell, “History of the High School for Negroes in Washington”, Jour nal of Negro History, Vol. 2, No. 3(July 1917), p.262.
59Department of Defense, Black Americans in Defense of Our Nation(Washington: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85), p.153. 60Mary Church Terrell, “History of the High School for Negroes in Washington”,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 2, No. 3(July 1917), p.264.
61Louise Daniel Hutchison, Anna J. Cooper: A Voice from the South(Washington:The Smithsonian Ins titution Press, 1981), p.62.
62第一名黑人联邦法官是William H. Hastie, 第一名黑人将军是O. Davis, 第一名黑人内阁成员是Robert C.We aver。
63Mary Gibson Hundley, The Dunbar Story, p.57.
64Alison Stewart, First Class: The Legacy of Dunbar, America’s First Black Public High School(Ch icago:Lawrence Hill Books, 2013), pp.91—93.
65Jervis Anderson, “A Very Special Monument”, The New Yorker, March 20, 1978, p.93.
66Ibid., p.113.
67见我的另一本书Black Rednecks and White Liberals。
68Jason L. Riley, Please Stop Helping Us, p.43.
69John U. Ogbu, Black American Students in an Affluent Suburb: A Study of Academic Disengagement (Mahwah, 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3), Chapters 1, 2.
70Ibid., p.179.
71Jason L. Riley, Please Stop Helping Us, p.45.
72Ibid., p.46.
73Ibid., p.47. 74数据见我的文章 “Assumptions versus History in Ethnic Education”,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Volu me 83, No. 1(Fall 1981)。
75U.S. Census Bureau, “Table 4. Poverty Status of Families, by Typ.of Family, Presence of Related Children,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1959 to 2013”, downloaded on October 23, 2014:http://www.c ensus.gov/hhes/www/poverty/data/historical/families.html。
76John H. Bunzel, “Affirmative-Action Admissions:How It‘Works’at UC Berkeley”, The Public Int erest, Fall 1988, pp.124, 125.
77Richard Sander and Stuart Taylor, Jr., Mismatch: How Affirmative Action Hurts Students It’s Int ended to Help.and Why Universities Won’t Admit It(New York:Basic Books, 2012), p.154.
78这本书中有许多表格,但是没有一张表格区分了正常录取的黑人学生和在平权运动中降格录取的黑人学生。见 William G. Bowen and Derek Bok, The Shap.of the River: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Considering Race i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dmiss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ix—xix。
79Ibid., p.61, 259.
80Stephan Thernstrom and Abigail Thernstrom, America in Black and White: One Nation, Indivisible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1997), p.408.
81William G. Bowen and Derek Bok, The Shap.of the River, p.60n.
82其他实证研究和相关批评可见我的另一本书Affirmative Action Around the World: An Emperical Study(N 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52—159。
83Stephan Therstrom and Abigail Thernstrom, “Reflections on The Shap.of the River”, UCLA Law Rev iew, Vol. 46, No. 5(June 1999), p.1589.
84Mark H. Haller, Eugenics: Hereditarian Attitudes in American Thought(New Brunswick:Rutgers Uni versity Press, 1963), p.11.
85比如见Edward Alsworth Ross, The Old World in the New: The Significance of Past and Present Immig ration to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The Century Company, 1914);Francis A. Walker, “Methods of Restricting Immigration”, Discussions in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ume II:Statistics, Nati onal Growth, Social Economics, edited by Davis R. Dewey(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 1899); Kenneth L. Roberts, Why Europ.Leaves Home(Bobbs-Merrill Company, 1922);George Creel, “Melting Pot or Dumping Ground?” Collier’s, September 3, 1921, pp.9 ff。
86Rudolp.Pintner, Intelligence Testing: Methods and Results, new edition(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 1939), p.453.
87Carl C. Brigham, “Intelligence Tests of Immigrant Groups”,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37, Issu e 2(March 1930), p.165.
88H.J. Butcher, Human Intelligence, p.252.
89For details, compare Carl C. Brigham, A Study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 versity Press, 1923), pp.16—19, 36—38;[Robert M.Yerk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sychol ogical Exam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rmy(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1), Vol. X V, Part III, pp.874, 875;Thomas Sowell, “Race and IQ Reconsidered”, Essays and Data on American Ethnic Groups , e d i t e d by Thomas Sowell and Lynn D. Collins(Washington:The Urban Institute, 1978), pp.226—227.
90James R. Flynn, “The Mean IQ of Americans:Massive Gains 1932 to 1978”,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95, No. 1(1984), pp.29—51;James R. Flynn, “Massive IQ Gains in 14 Nations: What IQ Test s Really Measur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01, No. 2(1987), pp.171—191.
91James R. Flynn, Where Have All the Liberals Gone? Race, Class, and Ideals 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72—74, 87.
92Robert William Fogel, The Escap.from Hunger and Premature Death, 1700—2100(Cambridge: Cambrid 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55—57.
93Robert William Fogel, The Escap.from Hunger and Premature Death, p.41.
94Kenneth L. Roberts, “Lest We Forget”, Saturday Evening Post, April 28, 1923, pp.3 ff;Kenneth L. Roberts, Why Europ.Leaves Home;Kenneth L. Roberts, “Slow Poison”, Saturday Evening Post, Feb ruary 2, 1924, pp.8 ff;George Creel, “Melting Pot or Dumping Ground?” Collier’s, September 3, 1921, pp.9 ff;George Creel, “Close the Gates!” Collier’s, May 6, 1922, pp.9 ff. 95Clifford Kirkpatrick, Intelligence and Immigration(Baltimore:The Williams & Wilkins Company, 1 926), pp.24, 31, 34.
96Philip E. Vernon, Intelligence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London:Methuen & Co., Ltd., 1970), p. 155;Lester R. Wheele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ntelligence of East Tennessee Mountain Child re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Vol. XXXIII, No. 5(May 1942), pp.322, 324;Hugh Gordon, Mental and Scholastic Tests Among Retarded Children(London:His Majesty’sStationery Office, 192 3), p.38.
97Arthur R. Jensen, “How Much Can We Boost IQ and Scholastic Achievement?”,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Winter 1969, p.95.
①例如,所谓的黑人英语与非洲毫无关联,反而与数个世纪前南方白人移民而来的英国某个地区有关。参见Davi d Hackett Fischer, Albion’s Seed: 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 ress, 1989),pp. 256—258。
②智商测验中美国南方白人的成绩较低与这一事实是一致的。即使不是大多数,至少也有许多南方人是来自英国 某些在文化上隔绝的地区,这些地区很晚才汇入英国的主流文化,曾被历史学家亨利·巴克尔(Henry Buckle) 称作“贫穷且无知”的苏格兰人促使苏格兰崛起并成为工业革命前沿也是后来的事情。参见Grady McWhiney,Cr acker Culture:Celtic Ways in the Old South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8),p. 56。
第5章 政治因素
1433年,大明王朝决定终止航海探险,并销毁船只和航海记录。这大概是人类文明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政治错误。朝中权臣党争促使他们做出了这一决定,无人为帝国的长远 利益着想。各类政府,不论是民主还是独裁,都可能染上这一致命的“疾病”。——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1
【注:隆庆开关呢??】
除了地理和文化这样的长期性或一般性因素,特定历史节点的个别偶然事件也会影响经济社会结果。15世纪的明宣宗决定将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这只是那些致命的政治决策中的一个。这些决策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影响,改变了一个文明的历史轨迹。偶然事件会打断地理或文化等一般性影响,抹灭地理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
西班牙政府资助哥伦布另寻一条经大西洋到印度的航线,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整个西半球国家的历史轨迹,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欧洲。倘若日本政府没有做出轰炸珍珠港的历史性决定,也就不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因美国的占领而引发深远的社会与制度变迁,那么今天的日本可能完全不同。
有时改变历史的偶然事件并非有意识的决定,它们可能是一场关键战役的结果,发生在混乱的战场上,交战双方在伯仲之间,结果却出乎意料。例如1815年的滑铁卢之战,胜 利一方的指挥官威灵顿公爵称之为“一场几乎失利的战斗”。但他对拿破仑的胜利决定了 整个欧洲大陆尚未出生的数代人的命运。
倘若希特勒不是一个狂热的反犹分子,那么美国不可能成为第一个拥有核弹的国家。因为当时世界很多重要的核物理学家都是犹太人,正是在那些为了躲避欧洲 “反犹运动” 而逃到美国的犹太物理学家的推动下,美国才有了曼哈顿计划。
不论地理、文化或其他影响因素如何作用,最终都会受到权力的制约——不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军事权力。野蛮人摧毁了罗马帝国,使西欧的经济、文化和技术水平倒退了数百年。有研究估计,西欧用了一千年才重新达到罗马帝国时代的生活水准。2
**政府有没有成型的机构、政府运行有没有效率以及政府制定的政策,都会影响一国的经济水平。今天我们视国家政府为理所当然,却忽视了中世纪的群落、氏族或部落社会花了很长时间才联合起来成立更大的集团,然后才有希腊、中国和法国这样的政治实体在世界舞台上崛起。 从我们今天的视角看,尽管中国作为国家很早就已成型,但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出现得很晚,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只是一瞬。更重要的是,国家的崛起不论是从时点还是完整性上看,都不均衡。我们需要考察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国家崛起的过程、速度以及完整性 上的差异带来了怎样的经济与社会影响。
国家的兴起
中国的建立比英国和法国早数个世纪之久,而欧洲国家的形成又比美国早几个世纪。并且,国家的形成并非不可逆转。罗马毁灭了迦太基,波兰和其他许多国家被更大的帝国 吞并,而其中一些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欧洲和中东帝国的分裂又得到重组。
人类超越古代的狩猎——采集模式,在中世纪形成了更大的政治体,其中既有政治方面的动机,也有经济方面的动机。更大的治理单元通常意味着有更大的力量保护整个社会或能够增进社会利益。部落或村庄无法生产和销售大量的商品,也不能利用专业化和规模 经济带来更低的单位成本和更高的收益。这通常只有大规模生产的企业与产业才能实现, 前提是有足够大的市场能够吸纳他们的产品。
【注:这块内容可以用来批驳肢解中国的言论。】
城市也能因专业化而受益,只要对于生产的产品而言本地市场足够大。这样一来,专业化生产的工人能集中全部精力于一种产品或一个生产环节,如印刷或织布。虽然今天还有少数国家是新加坡和摩纳哥这样“一城即一国”,但通常而言,城市只是国家兴起道路上的一个“小站”。
社会规模变大有利于经济与社会利益,但并不意味着大社会就会遍地开花。在某时某地,小集团自发聚合为大集团可能也会滞后于同时代的其他社会,于是小而脆弱的社会会被大且强的社会占领或奴役。
为什么不同社会合并为更大的政治单元的速度存在显著差异呢?一个原因是一些社会与其他社会的交往与互动不仅更频繁,范围也更大。这样他们的民众与统治者在长期中能了解其他社会,并与其他社会的民众与统治者合作,通过试错慢慢解决分歧,缔结能给双方带来更大利益的纽带,这样双方均有动力保持并加深纽带联系。
这一过程在地理上相互隔绝的地区可能很缓慢,甚至不会发生。如巴尔干山区、大洋上分散的小岛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这些相互隔绝的地区在沟通与交通上受限, 也就很难形成古代中国或罗马帝国这样规模巨大的国家,或者类似意大利或泰国这样中等规模的国家。
信任半径在大经济单元的建立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对于小社会集团聚合成大政治单元的速度与程度来说,信任半径也很关键。小型山区团体联合成大政府组织的速度就特别缓慢。一项地理研究指出,由于“各种障碍的存在”,“政治团结在山区的‘出生’艰难又缓慢”。3
山区分散的居民有各自不同的语言和方言,阻碍了哪怕是最简单的交流。4同样,不论是否属于同一文化,宗族、部落、宗教差异与地理隔绝一同造成了山区居民的相互隔绝。 在非常贫穷的山区,合作带来的经济收益很有限,这也降低了联合的激励。在较富裕地区, 合作与联合的回报要高得多,由于拥有不同的技能和非常不同的自然资源,贸易会使相关的交易方获益。
不论是在阿富汗,还是在美国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山区,家族、部落之间的不和由来已久。5地理分隔阻碍了山区居民发展出更大范围的信任关系或更大的容忍半径。用一位著名地理学家的话说,这种社会分隔带给山区人的是“微型版山地国家”和“侏儒共和国”。 6
严格来说,确实存在较大的山地国家,如阿富汗,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难以有效控制他们名义上的领地。大约一百年前,多山地的阿富汗被描绘成一个部落林立且不存在“统 一意识”的地区,甚至有人认为“阿富汗发展国民凝聚力的希望渺茫”7。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一评价仍然有其合理性。
偶尔,外国征服会将政治联合施加给分散的山地地区,或者这种征服的威胁会使他们建立起抵抗联盟。但这种暂时的联合极少永久化,也没有使这些分散的地区发展为独立国家。
在这一点上瑞士是个例外。尽管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有众多山脉8,使得生活在山中的人们也与世隔绝,但阿尔卑斯有巨大的山谷,有利于形成较大的聚集区,也有利于山区居民相互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联系。9瑞士还具有其他山区缺乏的可航行水路,如日内瓦湖和琉森湖形成的封闭水路,它们不像其他经过山区的河流那样直接冲泻而下。
山区国家通常很小,而南美安第斯山的印加帝国是另一个更让人震惊的例外。该国占地面积90.6万平方公里,是瑞士的20多倍,大约相当于法国和德国加起来那么大。10这是一片狭长而幅员辽阔的山间河谷,海拔稍低一些,适合发展农业11,也就形成了不同于其 他山区的地理环境。其他山区的居民被分隔成小社区,因为山谷中可耕种的土地数量有限, 而且地理障碍妨碍了人们的交流与交通。
不像其他缺乏大型可航行水路的山区,安第斯山有一个的的喀喀湖,它有100英里长,900英尺深,湖面超过3000平方英里。12环湖而居的人们可以相互沟通联系。的的喀喀湖被称作印加帝国的发源地13,该帝国首都库斯科城位于两条河流之间。
安第斯山的山谷中还有众多美洲驼,尽管体型小,但在欧洲人把其他负重动物带到该地区以前是当地主要的驮畜。西半球的其他山区没有这样的动物。在此环境下,印加帝国 在南美洲的西部崛起,并扩张成为一个南北长4000公里的大帝国。14
温带气候使得人们必定要在一年四季种不同的庄稼,并且储藏食物以越冬过春。而对于印加帝国,该地区特殊的气候条件带来了另一种挑战。它位于热带的狭长而高耸的安第 斯山脉,该地区气候不同于典型的热带或温带气候。虽然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的白天平均 高温大约为20~22.3摄氏度,但一年中不同时间降雨量迥异造就了季节性气候。
降雨的季节性,以及冬天夜间温度会降到凝固点以下,庄稼无力对抗这种干旱和霜冻,而且每一年的气候也会发生变化。这些因素使得印加帝国面临的生存挑战类似于温带地区 的居民。为此,他们创造了大型食物储藏设备网络,遍布广袤的帝国,并发明了储藏易腐食物的方法。15印加帝国的地理环境同温带地区一样,使其有必要发展自律性和广义上的 人力资本。从任何气候意义上看,印加帝国都不是一个热带国家。
瑞士和印加帝国的特殊地理环境使它们成为例外。通常山地的地理障碍会使山区居民贫穷、落后,无法建立强大而运行良好的政治组织。但是,导致隔离和阻碍国家形成的地 理特征并非只有山地一种。其他在地理上与世隔绝的地区,如加纳利群岛和撒哈拉以南非 洲的部分地区,在文化上也相互分隔,并且比起生活在宽广大陆上彼此容易交流的人群, 这些地区存在大量不同的语言阻碍了交流。
例如西班牙人发现加那利群岛时,当地人不仅贫穷落后,而且不知道有铁和其他金属。岛上的人群尽管与另一些岛上的人群同属一个种族,但使用的语言却完全不同,相互听不懂。16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们早在一千年前就学会了铸铁,但语言的多样性同样造成了交流的障碍。在地理障碍相对不严重的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部落规模比地理障碍严重 的地区大。就像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一样,这些更大更发达的部落经常会占领或奴役小而 落后的相邻部落。
中国的汉字有一大优势,它是一种非表音的文字,即使彼此不懂对方的方言,不同地区的人仍可以用书写来交流。政治上来说,这有助于各地语言不通的人形成统一国家。
权力是相对的,小政治单位能否存活取决于一定距离内其他政治单位的大小和势力。之前我们提到,政治统一的障碍使得小社会在面临征服和奴役时很脆弱。尽管美国存在一种广泛的误解,认为“奴隶制度是基于种族的”,事实上奴隶制在世界上存在的数千年里, 大多数情况下取决于谁更易受奴役,以及谁在攻击范围内。
欧洲人会奴役其他欧洲人,就像亚洲人奴役亚洲人、非洲人奴役非洲人一样。波利尼西亚人奴役其他波利尼西亚人,西半球土著也会奴役其他土著。“奴役”从词源上讲来自 “斯拉夫人”,在非洲人被欧洲人套上枷锁运到西半球之前,斯拉夫人已经被欧洲同胞奴役了数百年。17
欧洲人并非特意选择非洲人为奴,在世界其他地方拥有陆军和海军的国家兴起后,能够不花很大代价不需要冒很大风险掠夺奴隶的地方变少了,所以他们才会到非洲。抢夺奴隶在非洲持续了很久,主要是非洲人奴役其他非洲人,然后在西非把一部分奴隶卖给白人,最后这些奴隶被带到西半球。并且,船只航程增加和国家财富增多最终使得将大量奴隶从一个大洲运到另一个大洲在经济上变得可行。这就造就了西半球奴隶制的主导模式是奴隶和他们的主人在种族上不同。
这样一种模式不限于欧洲人占有非欧洲人。有许多相反的例子,除此之外,在地球上许多地方,奴隶和他们的主人都既非黑人也非白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缺少保护的欧洲海岸居民区和海上的欧洲水手都受到来自北非巴巴里海岸的海盗的侵扰,经常被掠去做奴隶。在1500—1800年间,巴巴里海盗奴役的欧洲 人超过100万。18这比运到美国殖民地(后来的美国)的非洲奴隶还多。19在奥斯曼帝国占领的东南欧,他们会把一定比例的男孩征兵为奴,让他们改变宗教信仰,训练他们,指派他们承担帝国中的民事和军事任务。20奥斯曼帝国的白人奴隶并非只有这些。奥斯曼帝国的富人喜爱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克斯妇女,他们纳这些妇女为妾。切尔克斯人也很珍视这个机会,当地母亲会极力推荐自己的女儿。21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政治联合步伐缓慢,留下了许多小且脆弱的社会。这些地方的人们被其他来自更有利地理环境的非洲人抢掠为奴隶,例如沿海地区的人奴役不发达且相互更分散的内陆地区的人。22白人从西非沿海地区的人手里买奴隶运到西半球。23 在东非,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会抢夺更脆弱的部落并奴役他们。24
少数群体或弱势群体的另一种命运是被征服。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帝国主义的后果之一是,帝国能够把被征服者组合成一个更大的政体,而这样大的单元远远超过征服者本身的能力。例如,罗马帝国将古代英国的独立部落合并成了不列颠尼亚,由一个统治范围涵盖该岛大部分地区的政府管理。四个世纪后,当欧洲大陆的罗马帝国本土受到攻击时, 岛上的罗马人为了保卫帝国撤走了。英国再次分裂为各个部落,经济上也倒退了。
这样的模式往往重复出现,罗马人撤退的一千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帝国主义在亚洲和非洲纷纷瓦解,各地也重新回归到分裂状态。例如,在尼日利亚被英国接管并组成尼日利亚之前,北方的富拉尼族部落和伊博人、约鲁巴族和其他部落从未联合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1960年英国殖民统治结束,尼日利亚获得独立,却深陷无休止的部落暴力冲突、可怕的内战以及一系列军事政变和反政变。所有这些都反映了部落间的敌对,当地土著自己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家,只能由外部的帝国统治糅合在一起。这种独立后陷入极化和暴力的模 式不止发生在尼日利亚。正如唐纳德·L.霍洛维茨(Donald L. Horowitz)在他关于国际 事务的著作《冲突的族群》(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中指出的:“在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独立团结让位于种族暴乱。”25
从地理上看,尼日利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相当幸运的地区之一。伟大的尼日尔河和它的主要支流贝努埃河灌溉了该国的土地,上天还赐予了尼日利亚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铁矿石和大量石油储备。西元前数百年,当地人就学会了炼铁,在英国人到来以前,当地就已经发展了自己的城市和国家,虽然规模没有英国统治下的尼日利亚那么大。而就在英国统治期间,尼日利亚部落间的敌对暂时被压制住了,但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根据霍洛维茨教授的论述: 殖民主义者对部落种族产生的真正深远且意义重大的影响,是改变了政体的规模,它如今是原来的好几倍。所有的殖民地都是人为的,它们的统治没有考虑种族构成,只是在范围上数倍于它们所取代或吞并的政治体系。26
就像一千多年前的罗马帝国统治英国一样,尼日利亚也是征服者人为建立的。一旦征服者退出,尼日利亚也就难以为继,更不用说繁荣兴盛。尽管尼日利亚没有四分五裂,但却是世界上最穷、最动乱的国家之一。这更多是政治的产物,而非地理障碍或尼日利亚人本身的缺陷造成的。这一点从生活在美国的尼日利亚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纪录可以看出 来: 2010年,美国约有26万尼日利亚人,占非洲裔美国人的0.7%。在2013年哈佛商学院的120名黑人学生中,尼日利亚人占到20%~25%。早在1999年,美国学院和大学的黑人学生中尼日利亚学生占比很高,是尼日利亚总人口在黑人总人口比例的10倍。27
接近四分之一的美国尼日利亚家庭收入超过10万美元。28即使考虑到移民与留在国内的人有所区别,在美国制度下,尼日利亚移民进步的方式与他们之前在母国制度下难以取得同样进步之间的反差,类似于与移民国外的印度人长期比他们母国的人们表现得更好。 这就启示我们,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近似的,即尼日利亚的政治结构和现状让该国居民及其地理环境的发展潜力化为乌有。
在亚洲,英属印度的国家规模更大,但情况非常相似。印度次大陆上生活的人群非常多样,出于统治的便利而被英国人一同纳入统治下,这一政体并非当地人在解决了相互差异与纷争后自发联合起来的。1947年英国人离开后,印度的杀戮更严重。随着英属印度分裂为印度教主导的印度和伊斯兰教主导的巴基斯坦,据估计有接近100万人死于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冲突。虽然这次分割旨在减少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冲突,此后印度和巴基斯坦仍然深陷内部各族群之间的冲突,最终东巴基斯坦独立,建立了新的国家孟加拉国。很多印度人移居他国,免受本土政治、约束、缺陷和冲突的影响,他们就像生活在美国的尼日利亚人一样,长久以来在世界各地都很成功。尽管印度普遍很穷困,但是印度裔美国人在美国统计调查局跟踪统计的各个群体中收入最高29(摩门教徒和犹太人这样的宗教群体没有被跟踪统计)。
其他多民族的后殖民国家在帝国瓦解获得独立后,也出现了类似的内部动荡。一部分国家,如印度、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分裂;而另一部分国家,如尼日利亚、 斯里兰卡和菲律宾仍旧保持统一,但经济和社会深陷内部冲突。 这种历史模式再次证明了与世隔绝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负作用,同样也告诉人们, 为什么过去两个世纪发生的交通运输与通信革命无法抹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隔离带来的影响。即使与世隔绝的地区也发生了彻底的交通与通信革命,那里的居民也无法赶上生活在文化域更广的地区的居民,因为在文化域更广的地方,居民千百年来熟知如何与其他居民合作,而那些生活在与世隔绝地方的人则无法这样做。
与世隔绝的人通常更贫穷,也更落后,这一事实也常常意味着交通与通信的最新进步对他们来说会有延迟,应用规模也更小。比如铁路这样的科技进步足以改变人生,19世纪上半叶,西欧各国就迅速建立了铁路,此后才传到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地区。
直到1860年,多瑙河和萨瓦河以南还没有铺设铁轨。30之前我们提到,1853年火车对日本人来说还是完全新兴的事物,当时日本又贫穷又落后。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塞尔维亚才有了第一条铁路。31而同时期,即使在美国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南部也建立了亚特兰大铁路枢纽,它是内战中威廉·T.谢尔曼(William T. Sherman)将军的部队穿越佐治亚州的摧毁目标之一。
帝国主义占领者建立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往往都很悲剧,这让人不得不怀疑由外来者建立国家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繁荣。按照美国最高法院的说法,种族多样性是社会力量的源泉,对政府来说是生死攸关的。32这一点被反复提及,但如今我们也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这一观点。很少有哪个词像“多样性”这样被持续不断地重复提及,却没有证据能支持它对经济或社会带来的所谓益处。相反,大量证据却证明它对社会和经济的害处。
人口多样性的支持者很少或从来没有对人口多样性国家承担的成本与获得的收益进行对比。印度的人口根据种族、语言、种姓等进行分类,可以分成很多部分。倘若多样性是优势,那印度相对于单一民族国家如日本应有很大优势才对。但很少有证据支持这种观点, 相反,却有很多反面的证据存在。如同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一样,印度没有哪一种语言的使用人口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不同族群的暴力冲突司空见惯。
**克服多种族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倘若能做到也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宣称多种族能够给一国带来净收益,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细细观察政治上单极化的多民族社会,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有许多让人头痛的问题。在一些国家,某个民族的人比其他民族更富有,这样的事实会被政治化。这些问题在此类国家很容易出现。 **
【注: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确实也是社会公敌!】
政治极化
许多因素会造成国家内部或国与国之间在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平等。但政治上流行的解释是将不那么幸运的人看作是更幸运的人的牺牲品。一般的解释因素,如地理、人口和文化,缺乏这种政治上的吸引力,不论它们对于造成这种差异的因果权重事实上有多大。
每一个社会,无论富裕还是贫穷,总有空间可以提高生产力。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也仅仅是“好像”。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穷国,倘若其中一部分群体比其他人有高得多的技能或经济活动的经验,并且这些群体在民族或社会特征上是不同的,就会产生重大的政治问题。
从经济视角看,这一状况呈现的是有价值的机遇,生产率更高的人能够通过提供急需的人力资本使得整个经济体变得更有生产效率,从而让所有人都受益。此外,拥有这样人 力资本的人能够促使社会中的其他人去掌握这种人力资本,他们可能通过示范学习,也可能通过与这一生产率更高的群体共同工作进行学习或在观察中学习,又或者是在学校学习这些技能。知识是少数“能够转移给他人而不会让留给自己的变得更少”的事物之一。
不过,从政治视角来看,问题就完全不同了。在第3章我们谈到,当生产率更高的群体在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会带来显而易见的不平等的经济结果,这会引发不太成功的群体的憎恨。许多落后国家的政治领袖对这种预期结果都早已知晓并且很敏感。
【注:追求“平等”本身就是脑残的想法!】
例如,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有一位政治领袖直率地指出:“不论马来人做什么,华人都能做得更好更便宜。”33这就为实施有利于马来人的特惠政策提供了政治上的合理性,即歧视马来西亚的华人。同样是这位政治领袖的观察: 有少数马来人渐渐成为富人,不是因为他们自身,而是由于政府的政策,这个政府得到了绝大多数贫穷的马来人的支持。似乎是贫穷的马来人付出的努力让他们中间少数被挑 选出来的人发财致富了,他们本身没有一丁点特殊的地方。但即使这些少数马来人不富起来,马来人中的穷人也仍然会一无所有。华人还是住大房子,认为马来人只能给他们当司机。由于这些少数富有的马来人的存在,贫穷的马来人就可以说,他们的命运不是注定要去服侍那些富有的非马来人。从种族自我意识的角度看,这一自我意识仍然很强烈,于是这些马来富人的存在也许不恰当,却非常有必要。34
这种反应包含的已经不只是贫穷或嫉妒那么简单,而是憎恨。如果问题仅仅是嫉妒,我们就很难解释马来人以他们富有的马来苏丹为荣。35这些苏丹比马来西亚的绝大多数华人更值得嫉妒,因为他们比华人更富有,他们的财富主要来自继承,而不是个人努力。但相比于继承,个人通过努力取得成就更有可能对他人的自我意识带来威胁。不只是在马来西亚如此,其他地方也如此。
【注:“华人还是住大房子,认为马来人只能给他们当司机。”哈哈!】
比如,美国的洛克菲勒的三位继承人曾被选为三个不同州的州长,而罗斯福家族的两名后代凭借继承的财富当选美国总统。反而是后来移民美国的亚洲人触怒了美国落后群体的自负。但这些亚洲移民许多是难民,他们在抵达美国海岸时没有什么钱,英语也很蹩脚, 他们凭借辛勤工作从社会底层爬到了中产阶层,他们的子女在学校里表现出色,然后又进入久负盛名的大学念书。美国那些落后族群却什么也没做,更抓不住属于他们的机遇。
亚特兰大的韩国移民当仓管员,平均每周工作63个小时,其中五分之一的人甚至每周工作长达80小时甚至更久。36纽约的韩国裔蔬菜水果零售商凌晨4点就到批发市场,以便挑选最好的瓜果蔬菜,并节省送货费用。37
来自这些亚洲家庭的子女在学校也表现出相似的工作伦理,但是他们优异的学业成绩却同样引发了憎恨,如同世界各国成功的成年人在落后群体中引发的憎恨一样。在美国纽约和费城的公立学校中,亚洲家庭的孩子经常遭受黑人同学的暴力,这种情况持续很多年了。38教育部门对此却充耳不闻,没有阻止此类学校暴力发生,媒体人也没有就此发表愤慨的社论。但是当知识界偏爱的群体受到苛待时,这些媒体人就会随意使用“种族歧视” 的标签。
【注:哎,文科生~新闻从业者~】
就像今天移民美国的亚洲人一样,过去不同时期移民到世界其他国家的犹太人、黎巴嫩人和日本人也无钱财傍身,但他们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本,最终凭借人力资本富裕起来。 而在他们之前就在此生活的当地人没有像他们一样很好地把握机遇,这些移民的成功于是引发了当地人的憎恨。这样的社会现象同样存在于一国内部,如一些群体迁移到别的地方 后富裕起来了,也遭到当地人的憎恨。印度各地的马尔瓦尔人和孟加拉人、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亚美尼亚人、尼日利亚的伊博人以及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都是这类社会现象的例子。 39
许多国家在政治上优先保护大多数群体的自负,而不是让经济体中拥有最好技能和天赋的人创造经济和其他收益。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后,北部的富拉尼人在政治上优先考虑的是赶走来自南部的伊博人,因为这些伊博人在英国统治时期占据了尼日利亚北部的专业和技能类岗位。虽然没有足够的符合要求的富拉尼人能够替代伊博人,但后者还是被逐出了尼日利亚北部,这一过程经常伴随着威胁生命的暴力冲突。结果北部尼日利亚只能雇用欧洲移民来顶替伊博人的位置。40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同盟国战败,罗马尼亚占领了同盟国的部分土地,这些地方的大学有些在文化上属于德国,有些在文化上属于匈牙利。罗马尼亚政府在政治上优先选择了将德国人和匈牙利人赶出大学,即使当时绝大多数罗马尼亚人还不识字,更无法代替这些德国人和匈牙利人。41类似地,20世纪70年代,乌干达驱逐了亚洲人,结果整个经济崩溃。那些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亚洲人在乌干达已经控制商业部门有好几代了,将他们赶走之后,乌干达人根本毫无能力取代他们。42
这些例子并不是孤立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知名发展经济学家彼特·鲍尔(Peter Bauer)长期研究第三世界国家,他发现这些国家都有一个普遍的趋势:“对生产率最高的群体施加迫害,特别是这些人属于少数群体时更是如此,有时甚至将他们驱逐。”43
不论生产率更高的少数群体怎样有益于穷国的经济,他们的成功伤害了落后的多数群体的自负,因此经常遭到落后群体的憎恨。在玻利维亚,当一位本土血统的恐怖主义者被 问到为什么参加恐怖活动时,他是这样回答的:“这样我的女儿就可以不再当你们的女佣 了。”4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哈布斯堡帝国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建国,这个全新的国 家的领导人将优待捷克人作为最优先的政治目标——这意味着歧视德国人。他们在接下来 的30多年里制造了一系列对捷克人和德国人来说都是悲剧的事件。45
如果根本问题是贫穷或嫉妒,那么只要提高经济体的生产率,并帮助不掌握技能的群体也掌握生产性技能就能解决问题。但对于处于难堪的低人一等地位的人,这两种做法都无法让他们停止憎恨。
对那些沉浸在憎恨情绪的人,仅仅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是不够的。从憎恨者的角度看,首要的是将处于更优越地位的人拉下来。将那些更幸运的人处死甚至还不够。要从身体上折磨他们,在人格上羞辱他们,要让他们极尽卑微。这是一种普遍的模式,不论暴力的对 象是菲律宾的华人、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纳粹德国的犹太人,还是卢旺达的图西人。
菲律宾的华人就是这样的群体之一。他们更高的生产率在经济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也因此招来了暴力攻击。一项国际研究指出: 菲律宾有数百万菲律宾人为华人工作,几乎没有华人为菲律宾人打工。在社会的每个层面,华人都主导着工商业。全球市场的发展强化了华人的主导地位:外国投资者来菲律宾做生意,他们排他性地几乎只愿意与华人打交道。除了一部分腐败的政要和少数西班牙 混血贵族家族,所有的菲律宾亿万富翁都有华人血统。相反,所有从事低贱工作的都是菲律宾人,所有农民都是菲律宾人,所有家仆、所有住在寮屋的也都是菲律宾人。46
这项研究同时发现:“在菲律宾,每年被绑架的华人有上百人,几乎肯定是当地菲律宾人所为。即使支付赎金,许多被绑架者也被残忍撕票,其中有很多还是儿童。”47
【注:血债血偿!】
一项关于奥斯曼帝国的研究描述了1894年土耳其暴徒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包括“将男人刺死,强奸妇女,将他们的孩子摔死”。48 1915年又发生了一次针对亚美尼亚人 的死亡游行,数以千计的亚美尼亚人被杀死,许多妇女被强迫剥去衣服赤身裸体在城里游街示众。49 20世纪后期发生在卢旺达的事件也是类似的模式。胡图族人屠杀了数万图西族人。年轻的孩子在他们父母面前被杀害,先砍掉一只胳膊,然后是另一只。一位联合国官员报告 说:“接下来他们会割开这个小孩的鼻子,让他慢慢流血而死,在他死去之前割下生殖器, 并扔到他们惊恐万分的父母脸上。最后父母会被分尸杀死。”50
【注:实质上来说,这些行为其实都是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实践!】
类似的残暴行为代表了极度的憎恨和复仇心,不可能通过提高人均GDP来平复。可怕的报复性行动背后的感情不只是嫉妒心那么简单,更多的是憎恨,痛恨那些成功的人将难堪的低人一等的地位强加给他们并让他们受到伤害。
还有一个事实令人困惑和不安,一些群体对另一些群体施加可怕的暴行之前,曾友好和睦,甚至世代和平相处。只是后来后者变成了前者暴怒的对象。例如,《印度时报》 (The Times of India)曾提到,1992—1993年孟买爆发了族群暴力冲突,平日友好的邻居转眼就开始了血腥的杀戮。51
这种让人不安的模式提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问题,种族冲突表面上的缓和多大程度上表示局势趋于平稳?与此同时,这种模式也意味着恐怖活动或许需要一定的“催化剂”来 触发情绪。当然没有人能提前知晓什么时候“催化剂”会出现,即使在最平和的情况下, “催化剂”也可能出现,它可以是特定事件,也可以是一个技巧娴熟的煽动者。
1948年斯里兰卡独立后,该国和国外的观察家都认为主要的种族之间关系良好,甚至称得上是“热忱”。52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中,占人口多数的僧伽罗人和占人口少数的泰米尔人之间从未发生冲突。两个族群的精英阶层都受过良好教育并且西化了,和平居住在同一块西化的飞地上。
但是,斯里兰卡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后不到十年,一个名叫所罗门·班达拉奈克(Solomon Bandaranaike)的人通过鼓动占多数的僧伽罗人反对占少数但更富裕的泰米尔人登上了总理职位。他发动了族群极化运动,逐步升级为暴力冲突,最终引发了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内战,内战中双方的暴行难以言说。班达拉奈克就是斯里兰卡冲突的“催化剂”。 他本身并不属于愤恨的穷人,而是来自精英家庭,但他很擅长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鼓动他人的情绪。①
许多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讨论,就好像这些国家的根本问题是贫困,或是缺乏提高生活水平所必要的技能和知识。为了帮助这些国家进步,提供资金、设备和能带来技能的技术专家似乎是上策。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都已经拥有了发展本国经济所需的人力资本。然而这些国家存在着政治障碍,无法发挥国民的人力资本,也缺少激励,少数群体无法将他们的技能投入工作中,同时占多数的群体却缺乏这些技能,这就造成了两个群体在表现和收益上的差距。
世界各国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是不论是在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在经济上更发达的国家, 抑或是在多数群体技能更高超或少数群体技能更高超的国家,无一例外,那些追求领袖地位或落后群体选票的人都会给落后群体提供四样东西:
1.向他们保证,落后不是他们自己的错。
2.向他们保证,落后是他们嫉妒和憎恨的更先进群体造成的。
3.向他们保证,落后群体和其他人一样优秀,不会比其他人差。
4.向他们保证,与人口比例相匹配的社会经济利益和其他社会福利的公平份额是落后群体所需要的,也是他们应得的。有时还会附加某种对过去不公平待遇的补偿或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地之子”的特殊回报。
市场上的经济竞争会给予那些想办法脱离现实的人经济惩罚。选举中为选票进行的竞争会给予那些主张不同于流行观念的人政治惩罚。此外,种族领袖会不惜一切代价推动他们领导的族群隔离,即使事实已然表明全世界许多不同的人群之所以贫穷落后,主要因素之一正是隔离。
当落后群体聚居于一国特定区域时,这些群体的领袖会有动力脱离该国更发达的地区。如斯洛伐克人从捷克斯洛伐克独立,东巴基斯坦人从巴基斯坦独立并成立了新的国家孟加拉国。一旦他们不再是一个更发达国家的一部分,这些更贫穷的群体会在经济上受损,而 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则作为独立国家的领导人而获得更多的权力。后者也会全力鼓动作为独立国家的国民自豪感,而不去管这会让民众在经济上变得更好还是更糟。从精神层面看, 民众可以摆脱他人总是胜过自己所带来的公开的难堪和个人的耻辱感,从而获得精神解脱。
有些地区和国家不存在分裂的政治条件,落后族群的领袖会全力推动文化隔离。例如,即使西班牙裔儿童的父母愿意让学校用英语授课,以更有利于子女在美国经济和社会中爬升,但美国一些地方的法律或政策却要求西班牙裔子女必须用西班牙语接受教育。53
【注:中国政府将来可以逆向操作,全都逆向操作即可!】
在美国所有族群中,文化隔离程度最严重的是土著印第安人的后代,这些人仍生活在有高度法律自治权的保留地,人均收入不仅低于黑人和西班牙裔,也低于其他搬离保留地的印第安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离开保留地的印第安人构成了全部印第安人的绝对多数,其人均收入已略高于西班牙裔美国人;而仍聚居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人均收入低于黑人或西班牙裔美国人,甚至还不到美国平均水平的一半。54但是,美国印第安保留地的领袖仍充满对外界的猜忌,捍卫他们的特权,并不断在保留地印第安人中间推动隔离文化。
族群领袖总是愿意将落后群体的落后归罪于更先进的群体。而更先进群体对待落后群体也并非总是合适的或得体的,这就给了落后群体的领袖抱怨的机会,不管这种情形是不是由更先进群体和落后群体在经济、教育或其他方面存在差距造成的。 某些情况下,一些更先进的群体的确压制了落后群体的发展。但不能由于一个群体在经济和其他方面更成功,就想当然认为一切皆如此。在全世界许多国家,更先进群体对待落后群体并不友好,即便如此,这也不能证明没有了更先进的群体,落后群体在经济上会更好。
当古罗马攻占古代英国后,罗马人对待英国人非常恶劣。但这并不能说英国人的落后就是罗马人造成的。事实上,罗马人到来之前,英国就非常落后,在罗马攻占英国以及镇压大规模起义中,罗马军团以少胜多打败了英国军队。在镇压起义时,罗马人屠杀了上千名英国人,领导起义的女王为了避免罗马人的报复也自杀了。但到了现代,即使如温斯顿·丘吉尔这样的爱国者也会赞同:“我们要把伦敦城归功于罗马。”55因为古代英国人没有能力建造这样一座城市。
没有人相信奴隶制下的奴隶会受到优待,世界各地的种种记录都昭示奴隶遭受非人待遇。今天的非洲裔美国人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黑人有共同的祖先,但前者的生活水平比后者高出许多,这绝不是偶然。这个结果当然不能反过来证明奴隶制的正当性,就像罗马人占领西欧留下了文化遗产让西欧人的后代因此获益同样无法证明罗马人的残酷压迫是正当的。
今天的落后个体或群体的祖先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但不能自动将自身的落后归罪于此,而这种不公平待遇也带来了意外后果,即引进外来文化,使后代受益。将道德责难与不公平混同起来也许在政治上很有吸引力,但道德谴责并不能作为不公平的因果解释。尽管现在有一种倾向,人们从政治上特别是意识形态上将道德因素与因果因素混在一起来解释经济不平等,但世界各地的山区居民之所以贫穷,并不是因为有人到山上将他们的财富洗劫一空,而是他们本来创造的财富就不多。西班牙大规模劫掠印加帝国的财富是一种例外, 而非普遍规律。
**过去无法更改,这一点毫无疑问。历史和现今世界的情形都表明,建立和维持同代人之间的良好关系是怎样一种挑战。令人吃惊的是,许多人仍想象自己能够修正已死之人犯下的过错,并且没有意识到这将在活着的人中间引发新的危险的敌意。 **
福利制度
我们通常关注福利制度在物质上带给个体或群体福祉的影响。然而,它同样影响一国整体的生产力水平,进而影响民众的生活水准。此外,福利制度的影响并不止于经济,还会扩展到社会行为,对福利受惠者及与之互动的群体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并不完全来 自福利制度,也来自与福利制度相伴而生的社会愿景,这些影响会改变人们看世界方式。
福利制度愿景
西方国家先有福利制度愿景,并在政治上流行开来,然后才开始建立福利制度。因此,评估福利制度的影响,我们应当将这一愿景的影响及形成的相关制度与政策的影响纳入其 中。福利制度的愿景基于许多假设,其中有两点非常重要:(1)许多人深陷贫困“泥潭” 中,繁荣的社会有能力也有责任给予救济;(2)陷入贫困的许多人完全没有机会像其他后来富裕起来的人那样能够过上好的生活。
即使社会规则是公平的,也就是说针对每个人的评价标准和奖惩标准是相同的,出生在南布朗克斯区的人也不可能与出生在高雅的林荫大道街区的人一样成功,不论我们怎样定义成功都是如此。倘若公平被定义为“让出生在不平等社会环境中的人有同等的成功概率”,情况将完全不一样。基于这样的“公平”定义,古往今来的所有社会都是不公平的。
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Nicholas Kristof)曾在《纽约时报》上十分清晰地论证了福利制度的愿景:
美国成功人士常见的一个幻觉,是认为他们之所以在人生“赛跑”中获胜,是因为他们努力工作和智力过人。
事实上,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是他们出生在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父母爱他们, 读故事给他们听,让他们参加小联赛的各类体育运动,给他们办图书馆借书卡,送他们上音乐课。通过这些活动,让他们获得培育熏陶。从受精卵开始,这些中产阶级出身的子女就开启了成功的“程序”。56
就像个人、群体和国家所处的地理、人口和文化条件造成了经济前景不平等一样,个体出生和成长的社会条件也是不公平的。有史以来,人类便一直如此。毫无疑问,我们中有许多人不认同这种不公平,并且跃跃欲试想采取行动改变这种情况。他们会采取何种行动也将影响深远,但可以尝试的选项之一就是福利制度。
克里斯托弗先生对于这种人生的不公平现象如何反应?他批评那些人“既不自知自身 优势,又不关心他人的不幸”。他指责他们是“政界心胸狭隘的人,或说得好听点,是对 那些在生活中苦苦挣扎的人缺乏同情心的人”,认为“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有人会反对扩 大医疗补助计划和长期失业救济金计划,或对提升最低工资以便与通胀率保持同步等抱有 敌意”。57简言之,为了应对这种人生的不公平,克里斯托弗的方案是由政府将资源从更 富有的人手中转移给不那么富有的人。当然,他没有对此类福利政策及愿景的深远后果发出警告,同样也不懂得这些后果会让那些更不富有的人或整个社会的净收益更好还是更糟。
有一种假定认为,人们反对最低工资法纯粹是因为对穷人缺乏同情心,这种假定忽视了大量文献中提到最低工资法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包括失业的年轻男性增多,在街上游荡的年轻人对任何社会都不能算好处。
1938年,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法——公平劳工标准法案(Fair Labor Standards Act)——获得通过。但此后的十年间,战时通货膨胀提高了物价和工人工资,导致该法案中确定的最低工资比非熟练工人实际挣的工资还低。直到1948年,大部分地区的经济状况跟不存在最低工资法一样。当年十六七岁的黑人失业率低于10%。为了与通货膨胀水平同步, 最低工资不断提高,这一年龄段的黑人失业率自此之后从未降到20%以下,在1958年和1975年分别是27%和45%。58不论是农产品还是劳动,人为导致的价格高于市场供求决定的均衡价格,都会带来供大于求的商品过剩。这与有没有同情心毫无关系,这种过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由某一经济学基本原理决定的。
克里斯托弗及其他人都提出了这样一种常见的观点:“奴隶制及之后对黑人的压制,给黑人留下的遗产是家庭破裂。”59但是,在奴隶制废除后的一百年里,成长于单亲家庭的黑人儿童比例从未超过20世纪60年代福利制度大规模扩张后的30年间的比例。即便如此,人们仍轻率地不断重复着“奴隶制遗产”的观点,而无视福利制度带来的后果。
1960年,22%的黑人儿童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35年后的1995年,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的黑人儿童比例是52%,单亲爸爸抚养的比例是4%,还有11%的黑人儿童没有父母抚养, 加起来占全部黑人儿童的67%。60这一年,贫穷家庭中的黑人儿童缺乏父亲抚养的比例高达85%。61
支持福利制度的核心理由是贫穷。但贫穷这个词是不是有特定的含义?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具体的定义。一旦定义完成,“贫穷”一词就被限定住了,既不多也不少,它与过去的定义完全不同了,即便人们还是会将它与饥饿、衣衫褴褛、狭小的住所等画面联系起来。 而今天的美国,贫穷是由华盛顿的那些政府统计学家定义的。他们本身就是福利制度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对贫穷的定义是不太可能挑战福利制度愿景的。
举个例子,2001年低于美国官方贫困线的大多数人家里都有中央空调和一个微波炉。实际上,这些物品在2001年官方定义的穷人中间的普及率已经高于1980年在美国全部人口中的普及率。2001年大多数贫困家庭都装有有线电视,并且有至少两台电视机。到了2003年,这些家庭中接近四分之三拥有一辆汽车,14%的家庭拥有两辆甚至更多辆汽车。62过去的低收入人群居住在过度拥挤的小房子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今天官方贫困线以下美国人的人均居住面积甚至超过欧洲人的平均水平,更不要说超过欧洲的穷人了。63正如一 位多年研究拉丁美洲的学者所说的:“美国的贫困线是墨西哥的中产线。”64
这当然不是说,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下的美国人没有什么问题。这类人的社会问题很严重,甚至经常是灾难性的。但此类问题并不是由于物质匮乏,往往是社会退化的结果。如今,福利制度思潮日渐流行,并成为普遍的未经批判的意识形态,这种社会退化反映的是当今时代的社会逆流。65
进步与退步
非洲裔美国人群体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他们也经常被标榜为美国福利制度的受益者。但这种进步大部分,倘若不是绝大部分,发生在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对贫穷宣战”计划之前,该计划标志着美国大规模开展福利制度运动的开端。
对大多数黑人而言,进步可以从1863年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算起。黑人进步很缓慢但从未停止。到1900年,绝大多数黑人不再是文盲,而罗马尼亚人还要等数十年才能实现, 印度人更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能大规模扫除文盲。到了1910年,大约四分之一的黑人农民不再租种土地或不再是佃农,他们变成了土地的所有者或购买者。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 Gutman)的巨著《1750—1925年黑人家庭史:奴役和自由》(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 1750—1925)告诉我们,在1880年至1925年间,“典型的非洲裔美国家庭从社会地位看属于下层社会,并且由父母当家”。1925年,纽约黑人家庭中由不到30岁的妇女当家的仅占3%。66在福利制度扩张的年代,未婚少女妈妈变得很普遍。
找寻黑人贫困——尤其是早期真正的贫困——背后的原因并不困难。直到1930年,成年黑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6年,67大多是在比较差的南方学校完成的。那时,从年龄上算应该上高中的黑人孩子只有19%进入高中读书。68 1924年,第一所专为黑人孩子提供教育的永久性公立高中才在亚特兰大建成69,它是在当地黑人社区多年推动下才建立的。
1940年,有87%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由于大批黑人从美国南部迁到其他地区,黑人教育得到普及,也获得了更多城市工作的经验。到了1960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黑人家庭比例下降到47%,黑人贫困率下降了40个百分点。这一趋势发生在民权运动和20世纪60年代 “向贫穷宣战”的社会福利项目之前。在1960年到1980年的20 年间,黑人贫困率又下降了18个百分点70——下降也很显著,但速率变缓了。可见,新民权法案和福利制度的政策对于降低黑人贫困率的效果,并不如宣传的那样巨大。 1965年通过的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使得选举中产生了更多的黑人官员。但在推动黑人经济进步上,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法案没有带来类似的效果,甚至导致某些重要的社会层面开始出现退步。
尽管还有争议,这些社会退步中影响最大的是双亲家庭的减少。在第4章,我们已经看到,黑人教育因此退步,例如纽约史岱文森高中的黑人学生比例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 除此之外,犯罪暴力活动增多,包括贫民区骚乱,甚至一系列全国性的骚乱。第一起暴乱发生在洛杉矶,就在1965年投票权法案通过后的数天之内。
这起暴乱的爆发与当时流行的政治社会观念是矛盾的,这种观念不假思索地将黑人的问题归为白人不公正地对待黑人。尽管南方的法律条文和做法含有更普遍的种族歧视,但类似的暴乱在南方却不常见。71相反,最严重的一次暴乱发生在底特律,在这次暴乱中, 43人被杀死,其中有33名黑人。而底特律黑人失业率仅为3.4%,黑人的房屋拥有率也高于其他主要大城市72,但当时流行社会观念并没有关注这一事实。
黑人政治家和社区积极分子越来越多,也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种族领袖,推广他们的愿景,就像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种族领袖向他们所属的落后族群推广的愿景一样。这一愿景将落后族群的问题归因为其他族群施加的恶意行为。非洲裔美国人获得的答案在原则上也 与19世纪的波希米亚捷克人、20世纪的斯里兰卡僧伽罗人、新西兰毛里人等获得的一样: 加强族群团结,寻求集体政治解决方案,并抵制那些更富裕族群的文化。
与其他族群的其他处理方式相比,这种办法的真实运行轨迹究竟怎样?不论是在媒体上,还是在学术领域,这一点都没有引起黑人领袖、黑人或白人知识阶层的关注。全世界许多国家的族群——例如华人、黎巴嫩人、犹太人、日本人——从贫穷到富裕的崛起过程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成员在富裕后完全能够承担政治生涯所需的“奢侈” 支出,但他们很少作为族群的政治代言人开展政治活动。
【注:这里确实是很好的观察角度!】
长久以来,澳大利亚、巴西和美国的德国人以其不同寻常的政治冷漠而出名。他们的兴趣在于教育,以及其他能增进其经济地位的活动,这是他们最关注的。一些德国裔美国人——18世纪的穆伦贝尔格家族、19世纪的卡尔·舒尔茨和约翰·彼得·奥尔特盖尔德以 及20世纪的赫伯特·胡佛和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能够成为杰出的政治人物,并不是因为他们作为德裔美国社区的代言人,而是因为他们解决了全美国人民的问题。一直到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裔美国人都很少去投票。73即使在19世纪的波西米亚,当地的德国人在政治上受到攻击,他们最初的反应也是捍卫世界主义的价值观,然后才作为德国人群体去捍卫他们自身的利益。74
东南亚和西半球华人也同样如此,他们淡漠政治,专注于工作、教育和储蓄。这也许缺乏浪漫,但非常有效,也正是靠着这一点,犹太人、日本人和黎巴嫩人在移民他国时, 能够从贫穷慢慢走向富裕。在一国内部,这一做法也使得当地少数人口,如尼日利亚的伊博人、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和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族群崛起。
也有相反的情况,如爱尔兰人是美国政治上最成功的族群之一。但他们摆脱贫穷的崛起之路,并没有像其他不关心政治的族群那样迅速。爱尔兰政治家在19世纪中期开始占据美国一些城市的重要职位,几十年间主导了波士顿、纽约以及其他大城市的政治机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少数爱尔兰人因此获得了财富、地位和权势,但绝大多数爱尔兰人在经济上仍落后于其他美国人,甚至被一些移民群体甩在后面。
20世纪初,纽约的爱尔兰人有39%是非熟练工人,这一比例在当时纽约各族群中最高,另外有25%属于半熟练工。75同一时期,纽约的第一代爱尔兰妇女中有71%给别人当家庭用 人或私人仆人,到了第二代这一比例仍高达25%。76到1930年,能够支付得起超过100美元房租的爱尔兰人比例刚刚超过俄罗斯人(当时主要是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的一半,还不到德国人的一半。77需要指出的是,爱尔兰人大量移民到美国的时期比犹太移民早数十年,因此爱尔兰人在美国社会向上攀升的时间也更长。
落后的少数族群需要团结在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领袖周围,以便能够赶超领先的族群。不论这种观点看起来有多可信、有多鼓舞人心,历史告诉我们的却是相反的事实,成功的模式总是来自教育、工作技能以及家庭完整等因素,而不是政治。
尽管一些人很随意地用“奴隶制遗产”来解释今天黑人社区的缺陷,却很少有人去考察他们抱怨的事实,如没有父亲的家庭、犯罪率或其他社会弊病到底在哪个时期更糟糕,是奴隶制废除后的一百年里,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福利制度愿景胜出后。非白人中凶杀造成的死亡率——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是黑人被其他黑人杀死——在20世纪50年代大幅下降, 到20世纪60年代又开始上升。1950年,非白人男性中每10万人有45.5人是杀人犯, 1960 年下降到34.5人,到1970年却上升到了60.8人。78
双亲家庭的破裂造成了其他方面的退步,包括依赖政府福利生活的人所占比例上升79、失业率上升80、犯罪率上升81,以及在全国许多城镇中对白人和亚洲人的有组织暴力犯罪增多。82虽然黑人民权组织和黑人公众长期以来一直反对种族歧视,但在2013年的一项民意测验调查中,黑人认为黑人中的种族主义者多过白人。83
在20世纪上半叶,黑人从南方移居北方时,不会讲标准的英语,他们的其他言行也暴露出教育更低或思维简单,这些都受到北方黑人的嘲弄。黑人报纸和民权组织如“城市联盟”会试图帮助这些教育水平更低、阶层更低的黑人适应更大范围的社会规范84,就像移民时代的爱尔兰和犹太民权组织帮助他们的同胞所做的一样。85
文化多元主义主张所有文化在正当性上都是平等的,都同样值得赞赏。20世纪后半叶,这种未经批判的观念逐渐流行开来,拒绝贫民区文化的黑人被指责为“举止模仿白人”, 并被视作种族背叛。现在,即使是受过更多教育、更适应外部文化的黑人,特别是黑人青年,也觉得有必要吸收贫民区文化中的一些模式或习俗,或对这类文化表露好感,以显示种族团结,或仅是为了避免社会摩擦。简言之,文化适应过程已经逆转,对最小规模的那部分群体有利的贫民区文化,扩散到更大的社会范围,在许多方面造成了明显的社会倒退。
在反映20世纪上半叶黑人社区的电视纪录片中,当时的黑人比今天更贫穷,这些社区没有几辆汽车,但街头涂鸦或窗户防盗栏杆也更少。在20世纪上半叶,不论是哈勒姆区的居民,还是造访该社区的白人,都不会觉得受到威胁,而在如今的哈勒姆区和其他黑人社 区,这种危险的感觉却无处不在。
1920年年底,许多白人经常去哈勒姆区的娱乐场所或参加私人举办的庆祝活动直到凌晨,经常到快天亮才回到他们在下东区的家里。许多人都有私家车,音乐评论家卡尔·范·维克顿(Carl Van Vechten)经常造访哈勒姆区,喝得烂醉走到街上,随便拦下一辆出租车回到他位于西边第55大街的公寓。86 20世纪30年代初,米尔顿·弗里德曼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和他的未婚妻经常去哈勒姆区的萨沃伊舞厅跳舞,他晚年回忆说,当时不必担心被抢劫或被妓女搭讪。87一个居住在哈勒姆区并在曼哈顿中心剧院区演出的黑人女演员说:“在凌晨一点钟,我会乘上第八大道地铁,到达小山顶站下车。不论怎样,我都不会感到害怕。”88难以想象如今的哈勒姆区或全美国的其他贫民区还能如此。
非洲裔美国人社会的退步主要表现在公共房屋的环境中。这些住房肮脏不堪,充斥着犯罪和暴力活动,很多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单亲家庭就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中。这种情形在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司空见惯,但20世纪上半叶,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事实上,两个时期都有种族隔离,但后期与早期反差鲜明,后期的公共房屋对申请者不加判断就同意入住。 正如《纽约时报》报道的,回顾早期的纽约公共房屋项目,我们会发现:
没有闲置的发出恶臭的电梯,也没有被帮派控制用作毒品交易的楼梯间。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纽约市的大多数公共房屋有维护良好的走廊、公寓和地面,以及充斥着自豪感的社区氛围。89
前后对比,不是物质环境不同那么简单。在早期公共房屋中生活的人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下着雨的星期六,大家的房门敞开着。孩子们可以从一间公寓溜到另一间,看电视上演的劳莱和哈台的喜剧或《牛仔卡西迪》。90
当时并非所有人都能买得起电视机,但是住在公共房屋里的人倘若有一台电视机,即使开着房门也不会觉得不安全,这样他们孩子的朋友就可以过来同他们一起看电视了。②
【注:社区建设确实是国家建设的核心!】
当时费城的公共房屋也有类似的氛围,黑人经济学家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正是在公共房屋中长大的,他描述到:
回到20世纪40年代,当时我们的家并不像后来那样以毒品、谋杀和午夜枪战而闻名。 与今天相比,那时最明显的区别是居住家庭的构成。不像我的姐姐和我,我们一起玩的小 伙伴大多数是双亲家庭。也许有其他单亲家庭,但我没有遇见过。大部分孩子的父母都努力工作,不论是房屋还是院子,都保持得很好。91
当时,公共房屋的墙上也没有涂鸦。到了夏天炎热的晚上,人们还会睡在阳台上,公寓第一层的人则睡在院子里。相邻街区的老年人坐在街上,围着一个桌子下跳棋或打纸牌。 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还用不起空调。92后来的公共房屋和黑人社区的情形与之前完全不同:
枪战越发激烈,父母会让子女睡在浴缸里或床下,防止他们被流弹击中。居民要进入他们自己的房子、拿邮件或是乘电梯,都必须给提着枪的青少年进贡。许多人就像自己公寓中的囚犯,他们害怕遍布毒品空瓶、用过的避孕套和粪便的走廊,走廊里的灯也被抢劫犯和毒品交易者摘掉了。被忽视和遭到故意毁坏的建筑走向衰败和崩溃。有能力逃离的人早跑了,留在那里的更多是贫穷且萎靡不振的下层阶层。这些公共房屋越来越被其他一些美国人视作与世隔离且让人害怕的地方,它们已经成为瘾君子、暴力犯罪者和问题人士的避难所。93
公共房屋中的居民人口结构也跟早期有了很大不同:
有子女的家庭中,90%户主是妈妈,81%接受未成年儿童家庭补助计划的资助。据估计,1980年的时候,失业率高达47%。尽管芝加哥有超过300万人口,其中仅有约超0.5%的人居 住在罗伯特·泰勒之家。但整个城市中,“11%的谋杀案、9%的强奸案以及10%的恶性袭击 案都发生在这一片公共房屋中”。94
非洲裔美国人在教育成绩上的退步,以及表现为家庭瓦解、吸毒以及暴力犯罪活动上升的其他方面的退步,与英格兰下层白人的情况惊人地相似。从1960年开始,大西洋两岸都在经历此类社会退步。英格兰下层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并且与非洲裔美国人贫民区的变化非常相似。英国医生西奥多·达尔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曾在一家临近低收入者的公共房屋的医院和一座监狱里工作过。他写的《底层人生》(Life at the Bottom)一书是这方面的经典著作,详细记录了在英格兰发生的一切。
对于公共房屋,他的观察是“就我所知道的公共房屋所在的街区,公共空间和电梯都充斥着难以消除的尿骚味。任何能弯折的东西都变形了”。95这些房屋除了物理上的衰败, 还有相伴随的居民结构的社会退化。在英格兰低收入的白人社区里,未婚妈妈带着多个子 女生活很常见,这些孩子的爸爸经常不止一个,他们没有一个愿意在经济上或在其他方面 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支持。针对这些英格兰儿童的行为,达尔林普尔医生记录了一位50岁女士所遇到的麻烦。该女士独自生活在贫民窟,是他的一个病人:
这些孩子在她走出屋子时不停地嘲弄她,他们把臭狗屎放到她的邮箱里,以此取乐。 她早就不指望这些孩子的母亲会制止这些行为,因为她们总是站在自己孩子的那一边,将任何对他们行为的负面评价视作对她们个人的攻击。她们不去纠正孩子的错误,反而用进一步的暴力来威胁她。96
将臭狗屎丢进他人的信箱里,这种行为不只是孤立的越轨行为,更是在这群人中间普遍的“表达对社会不满”的方式。97在学校,他们会殴打那些认真学习的学生以表达不满, 这也是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孩子对待那些被指责为“举止模仿白人”的孩子的方式。在英格兰一些低收入群体中,孩子间的暴力冲突有时候非常严重,达尔林普尔医生就曾接诊过挨揍的孩子。98
在20世纪后半叶,类似的犯罪活动猛增。1954年的伦敦,人人都允许购买霰弹枪,当年发生的持械抢劫总数不过是12起,其中有8起所用的枪并非真枪。长久以来,英格兰以世界上最遵纪守法的国家之一而知名。虽然所有枪支购买都受到了严格限制,但持械抢劫总数在1981上升到1400起,到1991年上升到1600起。99一项学术研究发现,1957年之后的10年时间里,在严重犯罪中使用枪支的比例增加了100倍。100
知识阶层的社会观念在英格兰和美国均取得了胜利,这种观念不光是福利制度,还包括未加批判的对罪犯更宽大的态度。于是,英格兰的犯罪率跟美国一样,在下降了好多年之后,到20世纪后半叶突然又反转上升了。101这也是两国严重的社会退步模式的一部分。 一个不加批判的社会,普通人共有的礼仪变成了可选项,也就不再是通行的礼仪。
英格兰与美国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低收入移民的子女在学校的表现好于低收入本土家庭的子女。2013年英国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各种族和不同国家背景的孩子的测验成绩,这些孩子全部来自收入极低的家庭,他们有资格享受学校提供的免费午餐。
在此收入组中,来自非洲和孟加拉国移民家庭的孩子有接近60%的时间达到测验标准,来自加勒比海黑人移民家庭的孩子有不到50%的时间达到测验标准,而白人本土家庭的孩子仅有30%的时间达到测验标准。在诺斯利区,白人小孩的这一成绩低于伦敦区的黑人小孩。102
表面看来,各种族的教育成绩好坏在英格兰与美国的情况差别很大。但是在这两个国家中,来自另一种不同文化的孩子在学校中的表现都好于本土出生的下层社会的孩子,在 这一点上两国惊人地相似。人们通常用基因、种族歧视或“奴隶制遗产”等因素来解释非 洲裔美国人贫民区学校的教育成绩不合格,但这些都不适用于英格兰的下层白人。结果上看,两国却很相似。
英格兰下层白人和美国贫民区黑人之间的共同点,在于数代人都接受了福利制度观念的灌输,这一观念传递给他们的是受害者情结、抱怨不公以及由于重重障碍使得他们毫无成功希望的观念。福利制度观念受福利制度项目保障,这些项目却补贴了不利于经济生产性甚至具有社会破坏性的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移民家庭不同于那些本土出生的低收入家庭,他们没有受到这一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的子女无此负担,因而表现更好。达尔林普尔医生在《底层人生》一书中讲 道:“在我所在医院附近的公共房屋中有一些16岁的白人小孩,我还未见到有谁能算出9乘以7是多少的(我这么说毫不夸张),甚至3乘以7等于多少都会难住他们。”103这是一个曾培育出莎士比亚和牛顿这样的大师的民族,为何如今许多年轻人连最基本的数学计算都不会了?基因决定论难以解释这一点。“奴隶制遗产”说或种族歧视说也无法解释此现象。
在英格兰,虽然表现糟糕的白人学生来自低收入阶层,但用贫穷来解释并不充分。因为这些孩子与前几代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相比都退步了104,美国也是如此。达尔林普尔医生的父亲出生在一个贫民窟。但在那个更早的年代,即使是贫民窟的学校也会维持一定的教育水准,不像后来的学校那样造就一种抱怨不公的情绪或传递一种不公阻碍了成功之路的观点,以便迎合穷人。105相反,早期的学校努力使学生获得摆脱贫穷所需的人力资本。 106
福利制度给英格兰和美国带来的后果之一,是许多人由于能依赖其他人的产出来生活,因此不必开发他们自身的生产性技能——人力资本。它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损失不止包括通过福利制度项目转移给社会中非生产性成员的那些益处,还包括那些项目受助者掌握技能后能够创造的更多的产出。
除此之外,一个不加批判的世界也滋养了人们凭借补贴生活而养成的反生产性生活方式,给社会其他成员施加了非常严重的精神成本。特别是对那些由于经济成本过高无法逃离这些街区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在这些街区,福利制度项目及其相伴随的社会愿景使得人们不再受文明行为规范的束缚,行为变得有攻击性且给他人带来威胁。此外,福利制度还增加了监狱、吸毒康复机构以及被遗弃或虐待子女看护所等方面的开支。
政府统计学家将某一部分人定义为“生活在贫穷状态”中,并且在这一群体中推动一种“依赖性”的文化,这样的做法有诸多错误之处。对于政客来说,具有依赖性的投票选民很有价值,而陷入狂想症的选民——对社会上的敌人非常憎恨,假想这些敌人费尽心机要让他们一直在社会底层——对政客的价值更大,他们扮演这些假想中的被蹂躏者的保护神的角色,以换取他们手中的选票。
许多福利制度项目不只向官方定义的处于贫穷状态的低生产率的人提供支持,也服务于福利制度相关机构和政客的利益。美国的福利制度机构的工作岗位、预算及权力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大批依赖性人口。这些机构不仅通过广告宣传扩大福利制度的使用者,还会分派雇员到低收入社区的超市去告诉人们可以申请政府项目为他们的食品付款。 福利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帮助那些陷入不幸的人,因为人们无法把控这些不幸,但福利制度机构本身却成了“陷阱”,它们不仅给遭遇预料之外的不幸的人提供帮助,还给那些只是陷入暂时困境的人提供帮助,比如那些面临高昂医药费的人或丢掉工作的人。在美国的许多州,多种相互间缺乏协调的福利制度补助同时存在,总金额远远超过官方贫困线划定的收入水平,也超过这些低生产率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能挣得的收入。107很多人从疾病中康复或摆脱其他暂时性不幸后,深陷福利制度依赖症,重新回归劳动力市场可能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显著下降。
如果一个人能挣1万美元,却要损失政府提供的价值1.5万美元的补助,实际上是对收入所得征收了超过100%的隐性税。即使是不这么极端的情形,福利制度项目的受益人重新工作,也就丧失享受政府补助的资格,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面临的隐形所得税远远高于百万富翁。长期以来这种负激励众所周知,然而不论是受益于福利制度依赖性的政客,还是在福利制度机构工作的人,都没有动力去纠正这一问题。毕竟这只对其他人是一个问题, 这些其他人包括福利国家的受益人和纳税人。
我们已经看到,在许多国家,族群领袖是如何鼓动那些对他们有利却不利于他们所领导的群体的生产率的观念。在全世界各地,有很多从贫穷走向富裕的群体,但它们很少像仍处在社会底层的族群那样,有很多或很突出的族群领袖,这也许是它们之所以能走向富裕的重要原因。任何理性且消息灵通的美国人都能说出三四位黑人领袖,但他们很难说出一位亚洲或犹太群体领袖,且还能够将这些族群在经济上摆脱贫穷的成就归功于这位领袖。
有些人主张推动广义上的收入再分配和狭义上的福利制度政策,但他们通常忽略了福利制度也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在美国,处在最低的20%收入组的家庭大多数无人参加工作。108转移给他们的经济资源大多是非现金的住房补贴、医疗保险和其他补助方式。 因此,用货币收入来统计的不平等数据大大夸大了生活水平的不平等,特别是对那些在福利制度政策界定的贫困状况下生活的人口更是如此,从生活水平上看,差距其实没有那么大。
由于福利制度政策已经扩张到了允许更多人不必工作就能活下去的程度,因而这些人不必去挣钱或发展自身的人力资本。福利制度政策的支持者谴责不公平,却恰恰在推动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福利制度的观念对于建立和维持福利制度非常重要,它也给人们的态度 和行为带来了负面影响,正如它在英格兰和美国所表现的那样。当然,这并不是说福利制度政策在各个国家的影响都一样,也不是说每个国家的福利制度观念都相同。毕竟如同其他情形一样,各个因素相互间的作用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福利制度虽然提供了相同的机会,但这些机会与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族群的已有文化价值相互影响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亚裔美国人与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生活在同一个福利制度环境下,但没有屈从政策诱惑而变得不思进取。美国联邦政府庇护最长时间的族群是生活在保留地的美国印第安人,他们的人均收入比其他族群都低并且低很多,这并非偶然。
福利制度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群体之间面临着不同的文化环境。在瑞典、挪威、芬兰和丹麦这些国家,出生在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男孩成年时仍处在该收入组的比例低于美国。这可能反映了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福利制度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于美国。 109虽然这是有待实证研究检验的问题,但这种情形至少可以作为例证之一,即如同地理、 文化、人口和其他因素一样,福利制度也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而是与其他因素相互影响。 我们不必像美国一样将福利制度推而广之,也不必认为福利制度是独一无二的。
无所不在的受迫害情结、对不公的抱怨以及认为自己应该获得权利,所有这些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对他人的攻击。《冲突的族群》这本国际性研究著作指出,这种攻击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非常普遍,“其中压倒性的都是由落后族群发起,而先进族群成为种族骚乱的攻击目标”110。
20世纪60年代福利制度愿景取得胜利后,全美国各地就爆发了贫民区骚乱,完全符合这种模式。后来类似的骚乱又多次重复发生。最近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黑人有组织地在购物中心、公园和海滩等贫民区之外的公共场所攻击白人。
贫民区暴乱的导火索或多或少是对特定事件的自发反应,即便之后流氓暴徒加入蓄意破坏和洗劫的行列,或职业种族积极分子点燃暴民的情绪使得骚乱升级。而新型的有组织地攻击白人显然是早有预谋或协商好的。大量年轻黑人男性会突然聚拢在一起,形成人数上的优势,然后对随机挑选的白人拳打脚踢。
攻击者的情绪往往也是狂欢而非愤怒111,被攻击者则会遭受严重甚至致命的伤害。曾有受害者说:“我听到他们一边打人一边在笑。他们就像在郊外野餐吃着薯条一样。” 112然而,知识阶层中的一些人仍然用“爱惹麻烦的年轻人”这样的口头语来描述这群狂欢的年轻暴民。
类似的种族攻击已经在几十个城市和小社区发生,范围覆盖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每个地区。113不仅仅是攻击本身,媒体报道和政治反应也是类似的,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 概括最常见的反应:死不承认。
**当攻击的规模过大、过于频繁或广为人知而难以忽视时,媒体的反应必定是故意撇去种族方面的因素,114虽然这是攻击者最重要的特征。这些人把受害者说成“疯子”,或 借口说“这是为了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虽然这些年媒体报道了美国各地发生的此类攻击,但每一次攻击都被当作孤立的地方性事件,不过是非特定的“年轻人” 出于不明原因攻击非特定的“受害人”。 **
当监控揭露了攻击者和受害者的种族身份时,美国各地的市长和一个又一个社区警官都很快出面否认种族袭击。115媒体并不需要在一开始否认这些袭击遍布美国各地,因为几乎没有媒体系统分析过这些袭击。《投资者商业日报》(Investor’s Business Daily) 是唤起大众关注这类毫无缘由的有组织种族袭击的少数媒体之一:“黑人年轻人中的一些暴民在社交网站上组织起来,一起去抢商店、揍白人。”116 其他媒体也获得了相同的信息,但很少公开发布。
媒体曾短暂地关注过另一种形式的黑人袭击白人的方式——“击晕比赛”,它指的是攻击者对毫无防备的路人头部猛打一拳,目的在于将对方击倒,可能的话打晕对方。2013 年,发生在纽约地区的黑人攻击犹太人的系列袭击案突然引起了每个人的注意117,而在2012年出版的一本关于黑人对白人的暴力犯罪的书中已经有一章描写这类攻击,标题就是 “圣路易式的击晕比赛”。118尽管攻击者将这类攻击看作一场游戏,受害者却轻则受伤住院,重则丧命。在拳击赛场被击倒的人落在帆布拳击台上,而在城市街道上,被击倒者会摔在水泥地上。
对于此类种族攻击,许多人的态度是不承认或轻描淡写。他们或许相信这样做可以消除白人的反击,不至于升级为真正的灾难性种族战争。但这类攻击倘若得不到制止,是不太可能会停下来的,除非更广泛、更真诚地承认攻击的危险性,并通过公众给民选官员施加压力,促使他们采取更多实质性措施和更真诚的行动,而不是继续否认这些攻击的种族性。
一些人也许相信,不论是对非洲裔美国人还是对英格兰的低收入白人,同情这些更不幸的人的方式之一,是不去批判他们的出格行为,似乎免除某个群体遵守文明行为规范的要求,就能给他们及整个社会带来净收益。可野蛮行径在哪个社会都不能算是一种赠礼, 反过来用暴力对抗野蛮也不是。族群间的报复行为,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 捷克人报复德国平民119,或20世纪后半叶发生在斯里兰卡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之间的暴 力与反暴力冲突120,都是一部血泪史。没有人希望看到这一幕在美国重演。
听任有组织的种族袭击在美国继续下去甚或纵容其进一步升级,或许不过是延缓了一场更大、更暴力的种族反击和种族极端化,因为不论主流媒体怎样遮掩,关于此类事件的信息一定会扩散开来。但就像对待其他事情一样,政治上对此类事情的反应通常是能拖就拖,即使这意味着未来的清算规模更大,会带来更具灾难性后果。除此之外,太多人在福利制度愿景中获得了太多既得利益——物质上的、政治上的以及观念上的,他们不愿将福利制度项目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加批判的观念,与广泛轻率的扩张的物质利 益相权衡。
今天的许多美国人都很难想象一群白人暴徒攻击黑人。但在100年前,特别是20世纪的前20年里,“种族骚乱”一词就是指的此类现象。121直到1935年,黑人发起的第一起大规模种族骚乱发生在哈勒姆区,情况才发生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黑人引发的骚乱成为常态。在此之前事情可不是这样,以后也可能并非如此。一旦预言成为现实,它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是所有后果中最微不足道的。
注释
1Freeman Dyson, “The Case for Blunder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6, 2014, p.6.
2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 eacon, 1957), p.45.罗马帝国没落后的数个世纪里, 有一些具体的衰退案例, 可见 Bryan Ward-Perkins,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z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pters V, V I;N.J.G. Pounds,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70, 71, 86, 165, 373—374;N.J.G. Pounds,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 1800—1914(Cambri 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46;James Campbell, “The End of Roman Britain”, The Anglo-Saxons, edited by James Campbell(Oxford:Phaidon Press, 1982), p.9。
3Ellen Churchill Semple,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 1 911), p.523.
4Ibid., pp.595, 596. Alton C. Byers, et al., “Introduction to Mountains”, Mountain Geography: Ph ysical and Human Dimensions, edited by Martin F. Price, et a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p.2;James S. Gardner, et al., “People in the Mountains”, Ibid., p.276.
5比如见Ellen Churchill Semple,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 pp.237, 591, 593, 599;J. R. McNeill, The Mountains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New York:Cambridge U niversity Press, 1992), p.48。
6Ellen Churchill Semple,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 pp.592, 593.
7Ibid., p.597.
8James S. Gardner, et al., “People in the Mountains”, Mountain Geography, edited by Martin F. Pr ice, et al., p.288;Ellen Churchill Semple,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 p.535;Fernand B 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由Sian Reynolds翻译 (New York:Harper & Row, 1972), Vol. I, pp.41, 207。 9Ellen Churchill Semple,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 pp.535, 548.
10Gordon F. McEwan, The Incas: New Perspectives(Santa Barbara:ABCCLIO, 2006), p.3;The Economis t, Pocket World in Figures: 2014 edition(London:Profile Books, Ltd., 2013), pp.148, 150, 222.
11Gordon F. McEwan, The Incas, p.23;Jeffrey Quilter, The Ancient Central Andes(New York:Routled ge, 2014), p.32;Thomas E. Weil, et al., Area Handbook for Peru(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p.36.
12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2014(New York:World Almanac Books, 2014), p.696.
13Ellen Churchill Semple,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 p.374.
14Gordon F. McEwan, The Incas, p.3.
15Alan L. Kolata, Ancient Inc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28, 129—130;G ordon F. McEwan, The Incas, pp.84—85, 121—122;John H. Bodley, Cultural Anthropology: Tribes, St ates, and the Global System(Mountain View, California: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pp.21 5—216.
16Ellen Churchill Semple,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 p.419.
17Orlando Patterson, Slavery and Social Death: A Comparative Study(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 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406—407, note 172;W. Montgomery Watt, The Influence of Islam on Medieval Europe(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2), p.19;Bernard Lewis, Race and Slav ery in the Middle East: An Historical Enqui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1;Da niel Evans, “Slave Coast of Europe”, Slavery & Abolition, Vol. 6, Number 1(May 1985), p.53, no te 3.
18Robert C. Davis, Christian Slaves, Muslim Masters: 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Barba ry Coast, and Italy, 1500—1800(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23.
19Philip D. Curtin,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 69), pp.72, 75, 87. 20Jean W. Sedlar, East Central Europ.in the Middle Ages, 1000—1500(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 gton Press, 1994), p.97.
21Ehud R. Toledano, The Ottoman Slave Trade and Its Suppression: 1840—189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8, 59, 168, 171, 188, 189.
22R.W. Beachey, The Slave Trade of Eastern Africa(New York:Barnes & NobleBooks, 1976), p.182;R obert Stock,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A Ge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 third edition(New York:T he Guilford Press, 2013), pp.179, 180;Ellen Churchill Semple,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 nt, p.275;Harold D. Nelson, et al., Nigeria: A Country Study(Washington:U.S. Government Printin g Office, 1982), p.16.
23Martin A. Klein, “Introduction”, Breaking the Chains: Slavery, Bondage, and Emancipation in Mo dern Africa and Asia, edited by Martin A. Klein(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3), p. 10;James F. Searing, West African Slavery and Atlantic Commerce: The Senegal River Valley, 1700— 186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69.
24R. W. Beachey, The Slave Trade of Eastern Africa, pp.182, 183, 189.
25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in Conflic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5.
26Ibid., p.76.
27Amy Chua and Jed Rubenfeld, The Triple Package: How Three Unlikely Traits Explain the Rise and F all of Cultural Group.in America(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 2014), p.42.
28Ibid., p.43.
29Ibid., p.7.
30N. J. G. Pounds,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 1800—1914, pp.457—458.
31Walter Nugent, Crossings: The Great Transatlantic Migrations, 1870—1914(Bloomington:Indiana U niversity Press, 1992), p.84.
32Grutter v. Bollinger, 539 U.S. 306(2003), at 328, 329.
33Mahathir bin Mohamad, The Malay Dilemma(Singapore:Asia Pacific Press, 1970), p.25.
34Ibid., p.44.
35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in Conflict, p.226.
36Pyong Gap Min, Ethnic Business Enterprise: Korean Small Business in Atlanta(New York:Center fo r Migration Studies, 1988), p.104.
37Illsoo Kim, New Urban Immigrants: The Korean Community in New York(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 ity Press, 1981), p.114.
38Elissa Gootman, “City to Help Curb Harassment of Asian Students at High School”, New York Time s, June 2, 2004, p.B9;Joe Williams, “New Attack at Horror HS:Top Senior Jumped at Brooklyn’s T roubled Lafayette”, New York Daily News, December 7, 2002, p.7;Maki Becker, “Asian Students Hit in Rash of HS Attacks”, New York Daily News, December 8, 2002, p.7;Samuel G. Freedman, “Student s and Teachers Expect a Battle in Their Visits to the Principal’s Office”, New York Times, Novem ber 22, 2006, p.B7;Kristen A. Graham and Jeff Gammage, “Two Immigrant Students Attacked at Bok”, Philadelphia Inquirer, September 21, 2010, p.B1;Jeff Gammage and Kristen A. Graham, “Feds Find M erit in Asian Students’ Claims Against Philly School”, Philadelphia Inquirer, August 28, 2010, p. A1;Kristen A. Graham and Jeff Gammage, “Report Released on Racial Violence at S. Phila. High”, Philadelphia Inquirer, February 24, 2010, p.A1;Kristen A. Graham, “Other Phila. Schools Handle R acial, Ethnic Tensions”, Philadelphia Inquirer, February 4, 2010, p.A1;Kristen A. Graham and Jef f Gammage, “Attacking Immigrant Students Not New, Say Those Involved”, Philadelphia Inquirer, De cember 18, 2009, p.B1;Kristen A. Graham, “Asian Students Describe Violence at South Philadelphia High”, Philadelphia Inquirer, December 10, 2009, p.A1;Colin Flaherty, ‘White Girl Bleed A Lot’: The Return of Racial Violence to America and How the Media Ignore It(Washington:WND Books, 201 3), Chapter 5.
39Myron Weiner, Sons of the Soil: Migr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in India(Princeton:Princeton Uni versity Press, 1978), pp.45—46, 102—136;Mary Fainsod Katzenstein, Ethnicity and Equality: The Shiv Sena Party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in Bomba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8—29;Myron Weiner and Mary Fainsod Katzenstein, India’s Preferential Policies: Migrants, The M iddle Classes, and Ethnic Equal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p.114—115;Dav id Marshall Lang, The Armenians: A People in Exil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1), pp.3, 10, 37;David Lamb, The Africans(New York:Vintage Books, 1987), pp.307—308;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in Conflict, pp.46, 153, 155—156, 212—213;Donald L. Horowitz, The Deadly Ethnic Ri o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p.4—5, 195, 198.
40Larry Diamond, Class, Ethnicity and Democracy in Nigeria: The Failure of the First Republic(Syr 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50.
41Irina Livezeanu, Cultural Politics in Greater Romania: Regionalism, Nation Building, & Ethnic St ruggle, 1918—1930(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18—231.
42Martin Meredith, The First Dance of Freedom: Black Africa in the Postwar Era(New York:Harper & Row, 1984), pp.229—230.
43P.T. Bauer, Reality and Rhetoric: Studies in the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London:Weidenfeld an d Nicolson, 1984), p.46.
44Amy Chua, 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 tability(New York:Doubleday, 2003), p.50.
45Derek Sayer, The Coasts of Bohemia: A Czech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 8), pp.168—169, 221—248.
46Amy Chua, World on Fire, p.4.
47Ibid., p.2.
48Lord Kinross, The Ottoman Centur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Empire(New York:William Morrow, 1977), p.558.
49David Marshall Lang, The Armenians, pp.31, 34. 想要完整地了解这些暴行, 可见Ambassador Morgenthau, 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02—223。
50“To Hell and Back”, The Economist, April 5, 2014, p.53.
51“Devils and Enemi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ly 7, 1994, p.53.
52正如一位斯里兰卡学者描述的:“与南亚其他地方(包括缅甸)形成鲜明对比,1948年的斯里兰卡是一片安定 有秩序的绿洲。权力的交接和平顺利,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民族运动温和的主线。更重要的是,斯里兰卡没有出现 南亚其他国家在独立过程中遇到的分裂和痛苦。总体来看,斯里兰卡的和平独立似乎给这个国家的建设和革新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K. M. de Silva, “Historical Survey”, Sri Lanka: A Survey, ed. K. M. de Silva (Honolulu: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7), p.84。“1948年斯里兰卡独立的时候,她的前景远比 大部分新成立的国家都好。” Donald L. Horowitz, “A Splitting Headache”, The New Republic, Februar y 23, 1987, p.33。“大体来看,锡兰的主要社区都很友好,印度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之间的冲突没有影响锡兰。 除了1915年发生的一场悲惨的小插曲,锡兰并没有出现种族动乱的预兆。” D.S. Weerawardana, “Minority P roblems in Ceylon”, Pacific Affairs, Vol. 25, No. 3(September 1, 1952), p.279。同时见Robert N. Kearney, Communalism and Language in the Politics of Ceylon(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7。
53Linda Chavez, Out of the Barrio: Toward a New Politics of Hispanic Assimilation(New York:Basic Books, 1991), p.29;Rosalie Pedalino Porter, Forked Tongue: The Politic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second edition(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6), pp.33, 35.
54Randall K. Q . Akee and Jonathan B. Taylor,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on American Indian Reserv ations: A Databook of the U.S. Censuses and the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1990—2010(Sarasota, F lorida:Taylor Policy Group.Inc., 2014), pp.6, 7, 16.
55Winston S. Churchil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London:Cassell and Company, Lt d., 1956), Vol. I, p.31.
56Nicholas Kristof, “Is a Hard Life Inherited?”, New York Times, August 10, 2014, Sunday Review section, p.1.
57Ibid.
58Walter E. Williams, Race and Economics: How Much Can Be Blamed on Discrimination?(Stanford:Hoo ver Institution Press, 2011), Table 3.2.
59Nicholas Kristof, “When Whites Just Don’t Get It”, Part 2,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7, 2014, Sunday Review section, p.11.
60Stephan Thernstrom and Abigail Thernstrom, America in Black and White: One Nation, Indivisible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1997), p.238. 61Ibid., p.237.
62Nicholas Eberstadt, The Poverty of“The Poverty Rate”: Measure and Mismeasure of Want in Modern America(Washington:AEI Press, 2008), Chapter 6.
63Robert Rector and Rachel Sheffield, “Air Conditioning, Cable TV, and an Xbox:What Is Poverty i 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Backgrounder, No. 2575, Heritage Foundation, July 18, 2011, p.10.
64Lawrence E. Harrison, The Pan-American Dream: Do Latin America’s Cultural Values Discourage Tru e Partner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New York:Basic Books, 1997), p.207.
65E. Franklin Frazier, The Negro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ised edition(New York:The Macmillan Co mpany, 1957), p.166.
66Herbert G. Gutman, 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 1750—1925(New York:Pantheon Books, 1976), pp.455—456.
67James P. Smith and Finis Welch, Race Differences in Earnings: A Survey and New Evidence(Santa M onica:Rand, 1978), p.10.
68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New York:Pantheon B ooks, 1975), Volume II, p.950.
69Henry Reid Hun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Secondary Schools of Atlanta, Georgia 1845—193 7(Atlanta:Office of School System Historian, Atlanta Public Schools, 1974), pp.51—54.
70Stephan Thernstrom and Abigail Thernstrom, America in Black and White, pp.233—234.
71Ibid., pp.159, 164—165.
72Ibid., pp.160, 162.
73Frederick C. Luebke, Germans in Brazil: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Cultural Conflict During World War I(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64, 66.
74Gary B. Cohen, The Politics of Ethnic Survival: Germans in Prague, 1861—1914, second edition(W est Lafayette: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pters 1 and 2.
75Lawrence J. McCaffrey, “Forging Forward and Looking Back”, The New York Irish, edited by Ronal d H. Baylor and Timothy J. Meagher(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29.
76Stephen Steinberg, The Ethnic Myth: Race, Ethnicity and Class in America(Boston:Beacon Press, 1989), pp.154, 165.
77The New York Irish, edited by Ronald H. Baylor and Timothy J. Meagher, p.562.
78Charles Murray,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New York:Basic Books, 1984), pp.116, 256.
79Kay S. Hymowitz, “The Black Family:40 Years of Lies”, City Journal, Summer 2005, p.21.
80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art I, p.135;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14(Washington: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4), p.380;Walter E. Williams, Race and Ec onomics, pp.42—43.
81Jason L. Riley, Please Stop Helping Us: How Liberals Make It Harder for Blacks to Succeed(New Y ork:Encounter Books, 2014), pp.67—73.
82比如见Katie DeLong, “He Thought It Was a Flash Mob:Man Caught up in Attack Outside Kroger Says He Feels Lucky He Wasn’t Hurt”, Fox 6 Now (Memphis), September 8, 2014;Therese Apel, “FBI to Assist in Allegedly Racially-Motivated West Point Beating”, The Clarion-Ledger (Mississippi), A ugust 27, 2014;“Family Thinks Otterbein Assault May Have Been Hate Crime”, CBS Baltimore, Augus t 25, 2014;Danielle Schlanger, et al., “Woman Hit in Head with Pellet Gun in Alleged Hate Crime While Walking Through Central Park”, New York Daily News, August 23, 2014;Steve Fogarty, “North Ridgeville Police Seek 3 Males in Assault of Teenager”, ChronicleTelegram(Elyria, Ohio), August 14, 2014;“Indiana Man Charged in Shooting Death of Gary Police Officer”, 5 NBC Chicago, July 24, 2014;Julie Turkewitz and Jeffrey E. Singer, “Family Mourns at Site of a Fatal Beating”, New Yor k Times, May 13, 2014, p.A14;Mark Morales, “68-Year-Old Man Dies a Day After He Was Beaten in E. Village;Video Captured Assault as Cop.Hunt Suspect”, New York Daily News, May 11, 2014;Paris Ac hen, “Two Men Held in Rose Village Gun Assault”, The Columbian(Vancouver, Washington), April 1 0, 2014;“White Man Beaten by Mob in Detroit After Hitting Boy with Truck:Was It a Hate Crime?”, CBS Detroit, April 4, 2014;“Police:Man Punches People in Face, Runs to Getaway Car”, KCCI 8 Ne ws.com(Iowa), February 24, 2014;Ed Gallek, “Mob of Teens Attack Man in Downtown Cleveland”, 1 9 Action News(Cleveland, Ohio), February 11, 2014;Wayne Crenshaw, “Victim Recounts Snow Day At tack at Warner Robins High;2 Arrests Made”, The Telegraph(Macon, Georgia), February 5, 2014;C arlie Kollath Wells, “NOPD Makes Arrest in Connection with French Quarter Beating of Musician”, The Times-Picayune(New Orleans), January 23, 2014;“Knock It Off”, New York Post, December 10, 2013, p.32;Thomas Tracy, et al., “Wild Bunch:Brooklyn Punks Pummel Couple, Scream out Slurs”, New York Daily News, October 20, 2013, p.13;Kaitlin Gillespie, “Police Seek Teens in Death of Wo rld War II Veteran”, The Spokesman-Review, August 23, 2013;“Father of Teen Charged in Florida S chool Bus Beating Says Son Is‘Sorry’”, Fox News, August 13, 2013;Peter Bernard, “3 Teens Char ged in Pinellas School Bus Beating”, WFLA.com, August 8, 2013;Jennifer Mann, “Man Convicted of Second-Degree Murder in St. Louis‘Knockout Game’Killing”, St. Louis Post-Dispatch, April 10, 20 13;Crimesider Staff, “Antonio Santiago Shooting:Suspects in Georgia Baby’s Murder Face First C ourt Appearances”, CBSNews.com, March 25, 2013;“Sauk Rapids Teen Charged as Adult in One-Punch Killing”, CBS Minnesota, January 7, 2013;Michelle Pekarsky, “Stone Murder:Metro Squad Will Dis band”, Fox 4 News Kansas City, May 15, 2012;Laura McCallister and Betsy Webster, “Men Beat and Rob World War II Vet”, KCTV 5 News, May 11, 2012;Michelle Washington, “A Beating at Church and Brambleton”, The Virginia Pilot, May 1, 2012, p.B7;WKRG Staff, “Mobile Police Expect to Make Ar rests in the Matthew Owens Beating Case Today”, WKRG(Mobile-Pensacola), April 23—24, 2012;Mic hael Lansu, “Officials:Trayvon Case Cited in Racial Beating”, Chicago Sun-Times, April 21, 2012, p.2;Chad Smith, “Gainesville Beating Case Drawing National Attention”, Gainesville Sun, April 1 0, 2012;Suzanne Ulbrich, “Father Searching for Answers in Son’s Attack”, Daily New(Jacksonvil le, North Carolina), April 7, 2012;Justin Fenton, “Viewers of Shock Video Shed Light on Baltimo re Assault;Tip.From Social Media Users Lead Police to Victim, Possible Suspect” Baltimore Sun, A pril 5, 2012, p.1A;Ray Chandler, “Seneca Police Referring Assault Case to Federal Authorities”, Anderson Independent Mail(South Carolina), March 28, 2012;Jerry Wofford, “Killing Ends 65-Year Romance”, Tulsa World, March 20, 2012, p.A1;Stephanie Farr, “‘Geezer’Won’t Let Thugs Ruin Hi s Walks”, Philadelphia Daily News, October 20, 2011, p.26;“Concealing Black Hate Crimes”, Inve stor’s Business Daily, August 15, 2011, p.A16;Barry Paddock and John Lauinger, “Subway Gang Att ack”, New York Daily News, July 18, 2011, News, p.3;Meg Jones, “Flynn Calls Looting, Beatings i n Riverwest Barbaric”, 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 July 6, 2011, pp.A1 ff;Josep.A. Slobodzian, “West Philly Man Pleads Guilty to‘Flash Mob’Assault”, Philadelphia Inquirer, June 21, 2011, p. B1;Mareesa Nicosia, “Four Skidmore College Students Charged in Assault;One Charged with Felony Hate Crime”, The Saratogian, December 22, 2010;Kristen A. Graham and Jeff Gammage, “Two Immigra nt Students Attacked at Bok”, Philadelphia Inquirer, September 21, 2010, p.B1;Jeff Gammage and K risten A. Graham, “Feds Find Merit in Asian Students’ Claims Against Philly School”, Philadelph ia Inquirer, August 28, 2010, p.A1;Alfred Lubrano, “What’s Behind‘Flash Mobs’?”, Philadelphi a Inquirer, March 28, 2010, p.A1;Ian Urbina, “Mobs Are Born as Word Grows by Text Message”, New York Times, March 25, 2010, p.A1;Kirk Mitchell, “Attacks Change Lives on All Sides”, Denver Pos t, December 6, 2009, pp.A1 ff;Alan Gathright, “Black Gangs Vented Hatred for Whites in Downtown Attacks”, The DenverChannel.com, December 5, 2009;Kirk Mitchell, “Racial Attacks Part of Trend; Gangs Videotap.Knockout Punches and Sell the Videos as Entertainment, Experts Say”, Denver Post, November 22, 2009, p.A1;Samuel G. Freedman, “Students and Teachers Expect a Battle in Their Visi ts to the Principal’s Offic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2, 2006, p.B7;Colin Flaherty, ‘White Girl Bleed A Lot’, 2013 edition。
83Rasmussen Reports, “More Americans View Blacks as Racist Than Whites, Hispanics”, July 3, 2013; Cheryl K. Chumley, “More Americans Say Blacks More Racist Than Whites:Rasmussen Report”, Washin gton Times(online), July 4, 2013;Steven Nelson, “Poll Finds Black Americans More Likely to Be Seen as Racist”, U.S. News & World Report(online), July 3, 2013.
84James N. Gregory, The Southern Diaspora: How the Great Migrations of Black and White Southerners Transformed America(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5), p.123;Isabel Wilker son, The Warmth of Other Suns: The Epic Story of America’s Great Migration(New York:Random Hous e, 2010), p.291.
85Carl Wittke, The Irish in America(New York:Russell & Russell, 1970), pp.101—102;Oscar Handl in, Boston’s Immigrants(New York:Atheneum, 1970), pp.169—170;Jay P. Dolan, The Irish America ns: A History(New York:Bloomsbury Press, 2008), pp.118—119;Irving Howe, World of Our Fathers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6), pp.229—230.
86比如见David Levering Lewis, When Harlem Was in Vogue(New York:Penguin Books, 1997), pp.182—1 83;Jervis Anderson, This Was Harlem: A Cultural Portrait, 1900—1950(New York:Farrar Straus Gir oux, 1982), pp.138—139.
87Milton & Rose 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Memoir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 8), p.48.
88Jervis Anderson, This Was Harlem, p.344。我曾做过杂货店的送货员, 那家杂货店就在她所说的地铁站旁 边。我也常常工作到半夜,回家的时候要路过那个地铁站,但我从未遇到过什么问题。我那时候的体重还不到10 0磅。
89Lizette Alvarez, “Out, and Up”, New York Times, May 31, 2009, Metropolitan section, p.1.
90Ibid., p.6.
91Walter E. Williams, Up from The Projects: An Autobiography (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10), pp.6—7.
92Ibid., p.7.
93Robyn Minter Smyers, “High Noon in Public Housing:The Showdown Between Due Process Rights and Good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the War on Drugs and Crime”, The Urban Lawyer, Summer 1998, pp.573—
94William Julius Wilson, “The Urban Underclas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The New Urban Re ality, edited by Paul E. Peterson(Washington: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5), p.137.
95Theodore Dalrymple, Life at the Bottom: The Worldview That Makes the Underclass(Chicago:Ivan R. Dee, 2001), p.150.
96Ibid., p.164.
97Ibid., p.159.
98Ibid., pp.68—69.
99Joyce Lee Malcolm, Guns and Violence: The English Experie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 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68.
100Ibid., p.209.
101Ibid., pp.90—91, 164—167;James Q. Wilson and Richard J. Herrnstein, Crime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1985), pp.409—410.
102“A New Kind of Ghetto”, The Economist, November 9, 2013, Special Report on Britain, p.10.
103Theodore Dalrymple, Life at the Bottom, p.70.
104Ibid., pp.155—157.
105Peter Hitchens, The Abolition of Britain: From Winston Churchill to Princess Diana (San Franci sco:Encounter Books, 2000), Chapter 3.
106Theodore Dalrymple, Life at the Bottom, pp.155—156.
107Michael Tanner and Charles Hughes, The Work Versus Welfare Trade-Off: 2013(Washington:The Cat o Institute, 2013).
108U.S. Census Bureau, “Table HINC–05. Percent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s, by Selected Character istics within Income Quintile and Top 5 Percent in 2010”, from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dow nloaded on October 28, 2014:https//www.census.gov/hhes/www/cpstables/032011/hhinc/new05_000.htm.
109Mark Robert Rank, et al., Chasing the American Dream: Understanding What Shapes Our Fortunes(N 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92.
110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in Conflict, p.180.
111比如见Colin Flaherty, ‘White Girl Bleed A Lot’, 2013 edition, pp.iii, 2, 3, 5, 10, 14, 26, 28, 33, 35, 36, 91, 113, 196—197, 209。
112Ibid., p.113.
113比如见Katie DeLong, “He Thought It Was a Flash Mob:Man Caught up in Attack Outside Kroger Say s He Feels Lucky He Wasn’t Hurt”, Fox 6 Now(Memphis), September 8, 2014;Therese Apel, “FBI t o Assist in Allegedly Racially-Motivated West Point Beating”, The Clarion-Ledger(Mississippi)Au gust 27, 2014;“Family Thinks Otterbein Assault May Have Been Hate Crime”, CBS Baltimore, August 25, 2014;Danielle Schlanger, et al., “Woman Hit in Head with Pellet Gun in Alleged Hate Crime Wh ile Walking Through Central Park”, New York Daily News, August 23, 2014;Steve Fogarty, “North R idgeville Police Seek 3 Males in Assault of Teenager”, Chronicle-Telegram(Elyria, Ohio), August 14, 2014;“Indiana Man Charged in Shooting Death of Gary Police Officer”, 5 NBC Chicago, July 24, 2014;Julie Turkewitz and Jeffrey E. Singer, “Family Mourns at Site of a Fatal Beating”, New Yor k Times, May 13, 2014, p.A14;Mark Morales, “68-Year-Old Man Dies a Day After He Was Beaten in E. Village;Video Captured Assault as Cop.Hunt Suspect”, New York Daily News, May 11, 2014;Paris Ac hen, “Two Men Held in Rose Village Gun Assault”, The Columbian(Vancouver, Washington), April 1 0, 2014;“White Man Beaten by Mob in Detroit After Hitting Boy with Truck:Was It a Hate Crime?” CBS Detroit, April 4, 2014;“Police:Man Punches People in Face, Runs to Getaway Car”, KCCI 8 Ne ws.com(Iowa), February 24, 2014;Ed Gallek, “Mob of Teens Attack Man in Downtown Cleveland”, 1 9 Action News(Cleveland, Ohio), February 11, 2014;Wayne Crenshaw, “Victim Recounts Snow Day At tack at Warner Robins High;2 Arrests Made”, The Telegraph(Macon, Georgia), February 5, 2014;C arlie Kollath Wells, “NOPD Makes Arrest in Connection with French Quarter Beating of Musician”, The Times-Picayune(New Orleans), January 23, 2014;“Knock It Off”, New York Post, December 10, 2013, p.32;Thomas Tracy, et al., “Wild Bunch:Brooklyn Punks Pummel Couple, Scream out Slurs”, New York Daily News, October 20, 2013, p.13;Kaitlin Gillespie, “Police Seek Teens in Death of Wo rld War II Veteran”, The Spokesman-Review, August 23, 2013;“Father of Teen Charged in Florida S chool Bus Beating Says Son Is‘Sorry’”, Fox News, August 13, 2013; Peter Bernard, “3 Teens Cha rged in Pinellas School Bus Beating”, WFLA.com, August 8, 2013;Jennifer Mann, “Man Convicted of Second-Degree Murder in St. Louis‘Knockout Game’Killing”, St. Louis Post-Dispatch, April 10, 20 13;Crimesider Staff, “Antonio Santiago Shooting:Suspects in Georgia Baby’s Murder Face First C ourt Appearances”, CBSNews.com, March 25, 2013;“Sauk Rapids Teen Charged as Adult in OnePunch K illing”, CBS Minnesota, January 7, 2013;Michelle Pekarsky, “Stone Murder:Metro Squad Will Disb and”, Fox 4 News Kansas City, May 15, 2012;Laura McCallister and Betsy Webster, “Men Beat and R ob World War II Vet”, KCTV 5 News, May 11, 2012;Michelle Washington, “A Beating at Church and B rambleton”, The Virginia Pilot, May 1, 2012, p.B7;WKRG Staff, “Mobile Police Expect to Make Arr ests in the Matthew Owens Beating Case Today”, WKRG(Mobile-Pensacola), April 23–24, 2012;Mich ael Lansu, “Officials:Trayvon Case Cited in Racial Beating”, Chicago Sun-Times, April 21, 2012, p.2;Chad Smith, “Gainesville Beating Case Drawing National Attention”, Gainesville Sun, April 1 0, 2012;Suzanne Ulbrich, “Father Searching for Answers in Son’s Attack”, Daily News(Jacksonvi lle, North Carolina), April 7, 2012;Justin Fenton, “Viewers of Shock Video Shed Light on Baltim ore Assault;Tip.From Social Media Users Lead Police to Victim, Possible Suspect”, Baltimore Sun, April 5, 2012, p.1A;Ray Chandler, “Seneca Police Referring Assault Case to Federal Authorities”, Anderson Independent Mail(South Carolina), March 28, 2012;Jerry Wofford, “Killing Ends 65-Year Romance”, Tulsa World, March 20, 2012, p.A1;Stephanie Farr, “‘Geezer’Won’t Let Thugs Ruin Hi s Walks”, Philadelphia Daily News, October 20, 2011, p.26;“Concealing Black Hate Crimes”, Inve stor’s Business Daily, August 15, 2011, p.A16;Barry Paddock and John Lauinger, “Subway Gang Att ack”, New York Daily News, July 18, 2011, News, p.3;Meg Jones, “Flynn Calls Looting, Beatings i n Riverwest Barbaric”, 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 July 6, 2011, pp.A1 ff;Josep.A. Slobodzian, “West Philly Man Pleads Guilty to‘Flash Mob’Assault”, Philadelphia Inquirer, June 21, 2011, p. B1;Mareesa Nicosia, “Four Skidmore College Students Charged in Assault; One Charged with Felony Hate Crime”, The Saratogian, December 22, 2010;Kristen A. Graham and Jeff Gammage, “Two Immigra nt Students Attacked at Bok”, Philadelphia Inquirer, September 21, 2010, p.B1;Jeff Gammage and K risten A. Graham, “Feds Find Merit in Asian Students’ Claims Against Philly School”, Philadelph ia Inquirer, August 28, 2010, p.A1;Alfred Lubrano, “What’s Behind‘Flash Mobs’?”, Philadelphi a Inquirer, March 28, 2010, p.A1;Ian Urbina, “Mobs Are Born as Word Grows by Text Message”, New York Times, March 25, 2010, p.A1;Kirk Mitchell, “Attacks Change Lives on All Sides”, Denver Pos t, December 6, 2009, pp.A1 ff;Alan Gathright, “Black Gangs Vented Hatred for Whites in Downtown Attacks”, The DenverChannel.com, December 5, 2009;Kirk Mitchell, “Racial Attacks Part of Trend; Gangs Videotap.Knockout Punches and Sell the Videos as Entertainment, Experts Say”, Denver Post, November 22, 2009, p.A1;Samuel G. Freedman, “Students and Teachers Expect a Battle in Their Visi ts to the Principal’s Offic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2, 2006, p.B7;Colin Flaherty, ‘White Girl Bleed A Lot’, 2013 edition。
114Colin Flaherty, ‘White Girl Bleed A Lot’, 2013 edition, pp.6, 14—15, 77, 83—84, 89, 94, 109, 133, 173—174, 178—179, 202, 203, 206.
115比如见Ibid., pp.i, iv, 3, 7—8, 84—85, 88, 95, 112, 192, 220。
116“Concealing Black Hate Crimes”, Investor’s Business Daily, August 15, 2011, p.A16.
117比如见“Brooklyn Rabbi:Gang of Teens Playing Disturbing Game Of‘Knock Out The Jew’”, CBS Ne w York, November 12, 2013;Thomas Tracy, “Jews Target of Twisted Street Game”, New York Daily Ne ws, November 13, 2013, p.45;“Knock It Off”, New York Post, December 10, 2013, p.32;Colin Flahe rty, ‘White Girl Bleed A Lot’, 2013 edition, pp.144—145, 151, 330。 118Colin Flaherty, ‘White Girl Bleed A Lot’, 2013 edition, Chapter 2.
119比如见Norman M. Naimark, 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Cambrid 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17—119;R. M. Douglas, Orderly and Human e: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 2), pp.96—97;Derek Sayer, The Coasts of Bohemia, p.243。
120SeWilliam McGowan, Only Man Is Vile: The Tragedy of Sri Lanka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 roux, 1992).
121Donald L. Horowitz, The Deadly Ethnic Riot, pp.19—20.
①班达拉奈克的目的达到后——成为斯里拉卡总理,他也愿意软化他鼓动的极端主义,但是他鼓动的情绪不会消去,会自发“生根发芽”。班达拉奈克在当选后缓和了反对泰米尔人的立场,但被一个佛教极端主义者暗杀了。 极化运动随后升级成毁灭性的内战。
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今天生活在官方定义的贫困水平的大多数人都用上了中央空调、有线电视,每一户都有多台电视机,但没有人敢敞开他们公寓的大门。
第6章 影响与展望
你怎样想的是你的权力,但不影响事实本身。 ——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汗 (Daniel Patrick Moynihan)1
与事实有关的问题显然不同于与价值、目标或政策相关的问题。对经济差异我们可以提出各种解释,并让这些论点接受事实的检验。而准确界定术语,以便阐明我们的分歧所在,这一点同样重要。对于问题有不同的观点在所难免,但需要澄清关于问题本身的混淆。
【注:本章也挺重要的,也是全章摘录的。】
收入与财富差异
个人、种族、国家与文明间存在的收入与财富差异原因何在?简单来说,这个问题没有单一的答案。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造成了这种不同。本书列举的影响因素并不全,相信也很难有人能将全部因素列出来。我们从已经考虑的那些因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不论是国家间,还是一国内部,都不可能取得均等的经济结果,因为造成这些结果的因素差别巨大。有一种关于“富裕社会中的贫穷悖论”的陈词滥调,这种悖论只是对某些人成立: (1)不顾历史事实,头脑中有一种关于公平世界的偏见;(2)没有考虑政府界定“贫穷” 的随意性。
当代福利制度的鼓吹者在推动公平时,主要致力于降低甚或消除群体间在收入或财富上的“不平等”或“差距”。但正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彼得·鲍尔指出的:“促进经济公平与减贫不是一回事,并且两个目标往往是冲突的。”2如果每个人的收入都翻倍,也就减少了贫困,但这同时会拉大收入差距与不平等。这一道理也适用于国家间和一国内部的差距与不平等。在物质层面,福利制度能够减少甚至消除贫困,但同时也会降低对人们凭借工作获取收入的要求,尤其如果人们通过工作获得收入后反而无法领取政府提供的各种福利,而这又会扩大收入差距和不平等。
【注:这个反驳理由确实充足~!】
在思考国家间经济差异时,人们经常提到一个问题,正如为人熟知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问的那样:“相比于美国,为什么埃及如此贫穷?究竟是什么阻碍了埃及人变富有?”3这种思考方式将美国的发展历程当作规范正常化、一般化,问题也就变成了埃及为什么没有实现这种正常化、一般化的发展。但从全世界看,过去几百年间,埃及而非美国的情形更具有典型性。
影响财富创造的因素非常多,它们有无数种排列组合,我们无法认为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埃及和美国一样。就好像埃及与美国发生龙卷风的频率不一样,因为影响龙卷风形成的因素非常多,它们相互作用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实际上,美国发生的龙卷风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多。4
美国形成龙卷风的地理特征或气候因素,从单个因素看没有什么是美国独有的,这些因素在其他地方都存在。例如,广阔的平原是形成龙卷风的因素之一,但在欧洲、阿根廷以及印度的很多地方都有平原。美国独有的是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龙卷风出现在美国中部而非沿海地区,它在一年中特定季节的午后比早晨或午夜更常见。龙卷风大都发生在美国的原因正是这些因素的组合。
倘若我们关心的是龙卷风的发源与活动情况,我们就不会去探寻为什么埃及没有那么多的龙卷风。与此相似,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去探寻埃及或其他国家贫穷的原因。贫穷尤其是绝对的贫穷是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命运。但是,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作者提出了一个更合理的问题:“在过去两百多年里,西欧、美国和日本比撒哈拉以南非洲、拉 丁美洲和中国更富裕,这一结果难道是由地理、文化或种族等因素而在历史上注定?”5
【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作者是个杠精,见识比索维尔差远了~】
虽然没有什么能保证一些国家或民众注定比另一些国家更富有,但还有一些因素会更容易加快或阻碍某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自与世隔离的山区、孤岛或其他地理上与人隔绝的地方的人,很难产生根本性的发展。数千年来, 澳大利亚被当作一个与其他大陆隔绝的典型,而澳大利亚土著也被当作落后族群的典型。
这或许对人类来说是普遍规律。不论个体还是小社会,倘若无法接触其他人口更多的群体,也就无法接触到其他群体的发展成就,更不可能攀上人类成就的“高峰”。测距仪曾用于航船,后来又用于相机。它的发明基于古希腊人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数学定理—— 勾股定理。①
【注:古埃及金字塔建造时不用勾股定理?古希腊文明作为古埃及文明的衍生物,为何能比自己老爷还厉害呢?】
不懂这种古代数学思想,以及后来其他地方和时代的人取得的进步,我们就很难凭空发明测距仪,更不用说完成更复杂的发明了。爱因斯坦如果不识字,生长在一个与世隔绝 的太平洋中部孤岛的原始部落里,他能提出相对论吗?即使是不那么惊天动地的科学进步, 也是基于无数前人的工作,甚至最终可溯源到数字和字母的发明者。这些人都来自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家。
追问“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是把成功看作常态,没有留意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成功只是偶然的例外。我们通常会对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身边的事习以为常,人类的这种天性容易理解。但即便如此,它们就是事实。在内战爆发前的美国,奴隶制被视作一种“特别的制度”。因为它与美国南方以外地区的准则与惯例格格不入。但不幸的事实是,对于全世界的无数人而言,奴隶制在数千年里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制度,普通人拥有自由才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它在历史上出现得非常晚。即使到了今天,这种制度还面临着风险,在一 些国家甚至被压制。
讨论财富、贫穷与政治,真正的挑战在于理解究竟是哪些环境因素使日本、西欧、美国及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实现富裕。即使在这些国家,这些因素的特定排列组合在古代也并 不存在。在古代,处于人类经济和发展前沿的是其他国家。
**贫穷是自发的,财富才需要创造,也需要解释。正因为如此,我们这里考察的是能够影响生产的因素,如地理、文化、人口和政治。有了生产就会有收入。这似乎理所当然, 但许多人把“收入分配”看作一个独立的有自我生命力的议题。对这类人,生产消失为暗淡的背景,就好像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收入模式而不抑制生产。但恰恰是生产决定了 我们社会的总体生活水准。将贫穷当作一个特别的问题来对待,并认为能通过扩展福利制度来解决贫穷,就像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发起的“向贫穷宣战”运动那样,反而会造成重大的社会影响,这一现象值得人们警醒。 **
考虑到与“收入分配”相关的基本统计数字被广泛误读,我们首先要澄清这些数字的含义。然后我们才能更细致地考察一国内部及国家间的收入差距背后的因素。
收入统计
显示收入趋势变动的统计数字有两类,它们在根本上不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完全相反。
其中一类统计的对象是固定的同一组人的收入,收集的是他们在研究期内的收入数据。媒体、政界和学术界经常引用的是另一类统计,它根据当年收入将人们分为5组:最高的20%、最低的20%以及处于中间的三组,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组别的收入进行统计。根据若干年的收入统计,得出每组人群的收入变动情况。
后一类统计数据经常被引用:相对于最低收入组(穷人组)或居于最低收入组与最高收入组之间的其他收入组,最高收入组(富人组)的收入都上升了。宣传“美国富人和穷人之间收入差距在扩大”的媒体比比皆是,包括《纽约时报》6和《华盛顿邮报》(Washi ngton Post)。后者的专栏作家E. J. 迪翁(E. J. Dionne)将富人刻画为“近年来收入猛增的一群人”,并指出政府对他们“课税不足”7。斯坦福大学的彼得·科宁(Peter C orning)所著的《公平社会》(The Fair Society)以及其他类似的书都在重复一个同样的主题:“我们社会最富有的人与最贫穷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迅速扩大。”8
媒体上充斥着类似的言论,政界和学术界也跟着附和。他们看起来比较的是“富人”与“穷人”这两类群体的收入,但事实上他们所比较的这两个特定群体的构成人员在不断变动。因为个体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会经历最初的入门级岗位,然后获得经验,再从事报酬更高的岗位,个体所处的收入组别会发生变化。与此类似,那些做生意的人或专业人士随着时间推移也会积累更多的客户资源,收入也会相应增加。
不同于跟踪个体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收入变化研究,有些研究跟踪同一个群体在不同时间的收入变动,它们得出的结论非常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跟踪了美国工人这一特定群体在1975年至1991年间的情况,发现相比于那些开始时处在最高的 20%的收入组的群体,处在最低的20%的收入组的人群在这些年间的收入增加了,不仅增加速度快于前者,而且增加的收入是前者的若干倍。9
基于这一情况,1975年处于最低的20%的收入组的人群到1991年时有95%已经提高了收入,甚至有29%的人提升进入了最高的20%的收入组,只有5%的人还留在这一收入组中。同一时期内,也就是1975年至1991年间,处于最高的20%的收入组的人群的真实收入提高幅度最小,不论是在百分比还是在绝对值上都是最小的。开始时处于最高收入组的人群平均收入增加的幅度还不到其他四组的一半。10
许多人大声呼吁:“随着时间推移,富人更富,穷人也更穷。”实证模式显然与此种论调不相符。人们刚工作时,只能从事入门级工作,收入也就处于最底层,但是经过不断历练,岗位提升,薪酬也就随之增加了,这一情形司空见惯。而已经人近中年的人此时生产率和收入都处于最高点,但两者的收入都难以进一步提高了。
后来的一项研究利用美国税务局的数据,发现了相似的模式。该研究跟踪了1996年到2005年十年间填报所得税申报表的个体。将这一群体分为5组,开始时处于最低的20%的收入组的人在这十年间收入增长了91%,意味着他们的收入几乎翻一番,而处于经常被提及的 “最高的1%”的收入组的人收入则下降了26%。11我们再次发现,事实与我们经常听到的论调完全相反,后者基于抽象的收入组别的统计数据,在讨论中假定这些收入组别是一组特定的有血有肉的人,却忽略了这些组别的构成个体在不断变化。
最近的一项研究跟踪了1990年至2009年间加拿大特定群体的收入变动,发现了与美国相似的模式。那些开始时处于最低的20%的收入组的人收入增速和增幅都高于其他更高的收入组别。12我们再一次看到,给定群体的收入变动与同一时间段内抽象组别的收入变动情况恰恰相反。同美国一样,加拿大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快于低收入组,也被当作是特定群体的收入变动趋势,人们忽略了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统计口径。13
简单地将抽象组别的统计数据汇总起来,得到的数据其实混合了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个体。而长期跟踪特定个体的统计调查成本更高,所以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其他众多统 计机构发布的数据,更多是对不同时间段内的抽象群体的调查,对特定群体跟踪调查的统计数据则很少。但是,这些抽象收入组在讨论中却被当作特定群体,如“穷人”和“富人”。各个收入组包含的群体都是变动的,个体在某时处于此组别,在另一时期又处于别的组别,但这些抽象的收入组却被当作包含了连续的个体。
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注本无可厚非,也值得称赞,但着迷于某一抽象组别中的成员的命运又是另一回事。有许多类似的言论,如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广受 赞誉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所说的: “收入最高的10%的群体自成一个小世界。”14这种观点全然不顾这样的事实,即很大比例的美国家庭(56%)在生命的某个时点(通常是他们年老时)都能进入“收入最高的10% 的群体”。15这样一来,嫉妒或憎恨“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其实是嫉妒或憎恨他们自身。这根本算不上“阶级冲突”,只是混淆了社会阶层与年龄组别。
在讨论收入差距的统计数据时,人们总是自然而然地将差异视作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而不是不同年龄的人群之间的差异。的确,几乎不会有人提到这些数字代表的究竟是不同社会阶层,还是不同年龄组的可能性。媒体在讨论中更是很少去思考他们讨论的是不同年龄群体还是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收入和财富统计数据引发了狂热的辩论,却很少有人准确定义这些数据,实际上它们完全起了误导作用。 从收入或财富看,未成年人少于他们的父母,它们的父母又少于他们的祖父母,这一点完全不同于个体在他们生命轨迹中的收入和财富变动情况。但是,人们却对后一种情况 更习以为常。统计上看,未成年人具有的收入或财富能够与他们的祖父母相同,但这只是统计把戏。即使限定为成年人,年轻人在统计上也能够拥有与年长者相同的收入或财富。 不同年龄群体的经济不平等与不同阶层间的经济不平等并非一回事。②
即使是媒体大肆讨论的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也有12%的美国人能在一生中的某个时点进入这一收入组。16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教授称之为“令人着迷的1% 圈子”17,但其魅力可能转瞬即逝。因为1996年还属于这个圈子的大多数人到2005年都已经掉出来了。18在皮凯蒂教授看来,收入处于最高的1%的人群不仅有自己的世界,而且 “在社会中鹤立鸡群”,对社会蓝图和经济政治秩序都施加了重大影响。19在他划分的社会等级以及“不平等结构”中,这一群体都高高在上。20
然而,结构与过程有着根本的区别。皮凯蒂掩盖了收入在生命不同阶段的变化过程,即使短短10年,个体的收入也会有很大区别。1996年至2005年间,超过一半的纳税人所处的收入组别都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的10年间情况也是如此。21例如,处在中间20%的收入组的人,有42%爬升到了更高的收入组,25%掉入更低的收入组,仅有33%维持不变。22
在最高收入群体中,成员的更替特别常见。10年间仅有不到一半的人仍能处在最高的1%的收入组。1996年处在最高的万分之一的收入组的人,到2005年仅有大约25%的人仍能留在此收入组中。23超过一半的人经过10年时间收入会减半,甚至大幅下降。24美国收入最高的400名纳税者——收入远高于最高的1%群体的整体水平——更替速度更快。从1992年到2000年,留在收入最高的400名所得税填报者中的时间超过1年的只有25%,在这9年间, 能留在这一超高收入组中超过两年的也仅占13%。25收入非常高的群体,不论是最高的1%、 最高的万分之一还是收入最高的400人,收入大部分来自投资收益,相比于工薪收入波动大得多。
简言之,虽然收入最高的400人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收入组的群体,但大多数只是瞬时最高收入。正如前面提到的,大多数人在9年中只有1年的收入大幅增加,也正是在这一年,他们的收入处在此水平,这或许是因为继承了一大笔财产,或许是将之前若干年积累的资产变现,又或许是其他原因。他们只在很短的时间内处于这一收入组,很难想象他们能够像一些论调传言的那样具有政治影响力。这并不是说不存在一直富有的人,这类人的生活方式的确完全不同于社会上的其他人。但他们与在特定时间跃入这一高收入组的人相同吗?那么,引用这些基于变动群体的数据,在讨论时看起来像是在讨论特定的人群,究竟意义何在呢?
皮凯蒂研究的重大过失在于,通过论述将流动的过程转化为僵硬的结构。在此结构中,收入最高的1%的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隔离开来,并控制和影响着整个社会。不论他的这一观察与流行的偏见是如何的一致,都脱离了显而易见的事实。 皮凯蒂的研究收集了众多国家的大量统计数据。但正如熊彼特早就说过的:“有的人游历四方,但改变不了他们戴着有色眼镜看事物的习惯。”26要检验皮凯蒂收集的统计资料的准确性是一个繁重的任务,或许也不值得为此花费时间和精力,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数字本身是否准确,而是对这些数字“究竟衡量了什么”的错误表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顺带指出,皮凯蒂不断重复说:“在赫伯特·胡佛总统任上,最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为25%。”但这与一份美国税务局的官方文件相矛盾,根据官方文件记录,1932年最高 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为63%。27
在讨论人们的经济差异时,引发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区分收入和财富,这两者有根本的不同,所以不能根据某一方面的统计数据,就敢信心满满地推断另一方面的情况。 使用“富人”标签来描绘更高收入组的人群,是混淆收入与财富的例子之一。因为,“富有”意味着拥有累积的财富,而不是简单的在某一年有高收入。这不仅仅是术语界定的问题。从实践层面看,提高所得税率以便让富人缴纳和他们财富相符的所谓 “公平份额” 的税收注定徒劳无功。因为所得税不是对财富课税。它是对正在积累财富的人征税,但那些通过个人劳作或继承已经完成财富积累的人将免于税负增加。
一些亿万富翁支持更高的所得税税率并因此获得赞美,这完全是赞美错了。提高所得税税率不会触动他们的亿万财富,相反会给其他纳税人带来沉重的负担。这些承受更高税负的人正努力挣钱积累财富,以便在他们离世时将财富留给家人。
【注:典~】
在大量关于“收入分配”的讨论中隐含着这样的观念,即某个收入组不仅在全部收入中占有更大的份额,而且是以牺牲低收入群体为代价。根据此观点,富人更富会让穷人更穷。《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尤金·鲁宾逊(Eugene Robinson)以及其他一些人都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富人正变得更富,这是以牺牲穷人和中产阶级为代价的。”这些非富人成为“上流社会”的“长期受害者”,后者正发动一场针对前者的“未宣战却具有毁灭性的战争”。28
鲁宾逊先生不经意间将一个无法经受事实检验的混乱观点公开化了。在他隐含的假定中,将收入组的收入趋势与“富人”和“穷人”这类由特定的人构成的群体的收入趋势并为一谈,而收入组其实是一群变动的人构成的。我们暂且撇开这一点,以便我们集中讨论其论点中的其他部分。
在某些时期,总收入中有更多份额归高收入组,但这不会阻止低收入组的真实收入在绝对值上的增加。例如,在1985年至2001年间,处于最低的20%的收入组的美国家庭所占份额从4%下降到了3.5%,但这一群体的平均真实收入增加了数千美元。这一情况还未考虑这样的事实,即初始在最低的20%的收入组的人大都在几年之内移动到更高的收入组。29 即使这些穷人仍停留在此收入组,“富人”收入的增加及所占份额的提升也不会让他们更穷,这一点可以得到数据的验证。
近年来,最低的20%的收入组的绝对真实收入增加了,而亿万富翁的人数也增加了。 根据尤金·鲁宾逊等人的说法,这些富翁的发达是以穷人为代价的,他们正在发动一场 “针对穷人的战争”。鉴于大多数收入处在最低的20%的家庭无人工作30,富人能从这些 什么都不生产的穷人那里拿走什么呢!
【注:典~】
随机假定
不论是国家之间还是一国内部,很少有什么因素能够保证经济生产的结果达到均衡,而今天的人们却坚信收入应该平等,并且视收入不平等(或称为收入差距、收入鸿沟、收入不公平)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邪恶的,这一点着实令人难以理解。在世界各地,人类活动的结果——不论是经济上还是其他方面——普遍存在着不均等的现象,并且很多都无法用歧视、剥削或其他恶行来解释。这些恶行确实发生过,但它们在道德上的意义并不能等同于它们和经济后果具有显著的因果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实证问题,但在“道德十字军”的绑架下,很少有人去追问答案。
人们总是相信,结果自然而然是均等的或随机的,并且人们普遍具有这种隐含假定,但它也带来了严重的道德、政治以及法律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仔细考察并用各种人类活动的事实来检验这一假设。我们在前面的章节提到,地理、人口和文化因素都是不平等的。此外,人的行为也不是随机的,而是带有目的性的。比如,从移民行为来看,这些移民不论是在移出国的来源地,还是选择移入国的定居地都不是随机的。养育子女的方式也不同,我们谈到过,在社会经济阶层不同的家庭里,子女从父母那里听到的单词量有多有少。
有目的的人类活动很少是随机的,造成的结果也是非随机的。种族、性别、宗教、出生顺序或其他因素的不同构成了不同的群体,各个群体的活动也不一样。
不论是经济活动还是其他方面,人类活动取得的成就可以有天壤之别,从最一般到最了不得。一项跨国研究考察了15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欧洲人文和科学史上的著名人物,发现这些人从来源地看分布很集中。“所有这些重要人物分布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内,这一区域不包括俄罗斯、瑞典、挪威、芬兰、西班牙、葡萄牙、巴尔干半岛、波兰、匈牙利、 普鲁士东部和西部、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大部分地区、意大利四分之一的低地地区和大约三分之一的法国地区。” 31
该研究同样发现,从美国建国到20世纪中期,美国大约一半的人文和科学领域的重要人物都集中在缅因州的波特兰到新泽西南端的弧形区域内。来自新英格兰各州、纽约州、 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美国人文和科学领域的著名人物,在数量上比内战期间构成邦联政府的那些州的7倍还多。南方州大多数都没有这样的人物,只有弗吉尼亚州是个例外。 32
不同个体在体育方面的成就也具有极大的差异。在职业高尔夫球手中,能够坚持到美国职业高尔夫协会锦标赛最后两轮而不被淘汰的选手,在每轮击球进洞数或击球距离指标上的分布接近标准钟型分布曲线。33但综合各种高尔夫技巧的终极测验,即赢得锦标赛冠军的分布是非常有偏的。
那些能不被淘汰进入最后两轮的选手,实力均高出平均水平,但其中有53%的选手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从未获得过一项锦标赛冠军,而其余47%获得过冠军的选手绝大部分赢得冠军的次数不超过3次。34然而,阿诺德·帕尔默(Arnold Palmer)、杰克·尼克劳斯 (Jack Nicklaus)和泰格·伍兹(Tiger Woods)三人每人都赢得过数十次冠军,加起来有两百多次。35
类似地,网球大满贯冠军、棒球击球冠军以及世界国际象棋冠军赛冠军的分布也非常有偏。362012年排名前100位的马拉松长跑选手,有68名是肯尼亚人。372014年全美拼写大赛第一名是两位印度裔美国人,他们打成了平手,不分胜负。这已经是第七次由印度裔美国人获得冠军,在前16届比赛中,有12次的获得者是印度裔美国人。38整个20世纪,大联盟棒球球员有8次曾盗垒达到或超过100次,所有这些球员都是黑人。39
学位获得者的分布同样有偏。20世纪早期,全美国有数以千计的大学和学院,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都出自美国东北部的8所常春藤大学。在2011—2012学年中,获得教育学学士学位的毕业生有接近80%是女性,而接近80%的工程学学士学位的获得者是男性。40
虽然非洲裔美国人的人口数远超过亚裔美国人,且黑人获得学士学位的人数也略高于后者,但在获得工程学学士学位的毕业生中,亚裔美国人比黑人的2倍还多。41在顶尖工程学院中,两者的差距更大,亚裔与黑人学士学位获得者人数比在MIT是3∶1,在哈维穆德学院是10∶1,在加州理工学院是40∶1。42然而,比起加州理工学院中亚裔和黑人群体的巨大差异,20世纪60年代的马来西亚华人和马来人获得工程学学位的人数差距有过之而无不及。华人在马来西亚是少数人口,马来人作为多数人口,不仅掌管着大学,而且控制着制定大学政策的政府。即便如此,华人学生获得工程学学位的人数超过马来学生的100倍。43
即使我们排除歧视因素,人类活动仍然具有无数类似的巨大差异,比如男人在许多方面胜过女人,又或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少数人口胜过占主导的多数人口。44
排除歧视因素的影响,各种人类活动的结果都不是均匀分布或随机分布的,但还是有人坚持这样的隐含假定:非平均的或非随机的结果看起来既奇怪又可疑。他们的这种看法并非随意的,因这类观点得出的结论在法庭上举足轻重。在这些案例中,“差别性影响” 的统计显示某些群体在人口统计中“代表不足”,并且与随机结果差别很大。媒体或学术界的知识分子将之视为歧视的铁证。无数事实证据都显示,各类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结果总体上既非平均的也不是随机的,但随机性的隐含假定完全无视这些事实证据。不仅如此,不管事实如何,很多严肃的法律与政策都建立在这一假定之上。
再分配主义者很少给出原则性的标准,也就无法判断当今的不平等是否正当。如今,很少有人敢说收入或财富应当绝对平等,他们只敢随意地宣称“当今的不平等程度太严重了”。
或许他们的说法可以总结为,当今的不平等程度超过了其他时代或其他地区,但他们没有说清楚是选择哪个时代或哪个地方作为原则性的参照标准。除此之外,被忽视的生产过程随时代不同而变化,对技能与天赋不同组合的需求也在改变,也就要求工资激励模式发生变化,吸引更需要的那些人。
这种变迁的一个典型例子,是随着机器越来越多地替代人力,体力劳动的价值降低了。这就使得男性在体力上的优势不那么重要,在同工同酬的法律通过之前,这一点已经缩小了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
近年来高收入与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报酬差距不断拉大,它既可能是阶层间的,也可能是不同年龄组之间的,但两者完全不同。在美国,户主年龄为25岁的家庭只有13%处于家庭收入最高的20%的收入组,而户主年龄为60岁的家庭,这一比例是73%。45既然每个人都从25岁到60岁慢慢变老,那么只要能活到美国平均预期寿命,人们就不会对不同年龄组收入差距的拉大感觉不公平。
在其他情形下,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拉大或许只是反映了相对于非熟练工人,社会对熟练工人特定技能的需求增加了;或者是相对于人力资源部门的经验,对金融专业知识的需求大大增加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或许同样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由于福利制度带给穷人的补助,有更大比例的人口不必为了谋生而工作,或只需要打零工做一些兼职就能生活。收入统计并没有包括这些补助,作为实物补贴——包括房屋补贴到医疗保险——其价值远超过最低的20%的收入组的货币收入记录。46
简言之,收入统计过度夸大了不同收入组的生活水平差距,因为这些收入数据(尤其是对低收入组)都是未缴所得税之前的,也没有考虑大规模的实物补助转移。
当然,并非所有的收入差距都是由年龄或政府福利造成的。但是,不论根源何在,生产活动对要素的需求是变动的。这意味着没有理由认为某一时代或某一地区的特定收入或财富差距模式不会变化,也没有理由把这一特定模式当作判断其他时代或其他地方的收入或财富差距的基准。
同样,知识分子或政治家每发现或提出一个人生的不完美之处就觉得应该对数百万人类同胞的生活施加控制,这也是毫无理由的。从“君权神授”时代以来,就有一种隐含假定,认为一部分人有剥夺他人自主决定生活的权力,这种权力往往声称是建立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的。
“社会正义”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巨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影响深远。在当代人中,他最好地阐述了有关收入与财富差距的道德准则。罗尔斯教授的“社会正义” 概念是指,“在社会系统中无论个体初始处于何种地位,亦即不考虑出生时的收入阶层, 拥有相同的天资与能力并且运用这些才能的意愿均等的人,在经济活动中具有的成功期望应当是相同的”。47
很少有人会反对这一理想情形,尽管每个人对现实这一理想情形的途径及可能性会有不同意见。但是,罗尔斯自己在提出这一理想情形后立刻进行了修正,加上了一个附加条件,即“自然禀赋更多的人所具备的优势应受到限制,以增进更贫穷群体的利益”48。因 为根据罗尔斯的观点,“正义优先于效率”49,就像出生就继承了大量财富一样,人天生的能力差异是不公正的,因而也是非正义的。
正如罗尔斯所言,非正义的回报只有在有益于“社会中更贫穷群体”时才会被接受,但这种言论容易引发事实性和道德性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如果根据收入来界定社会更贫穷群体,那么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年轻和缺乏工作经验的人,但他们的贫穷只是暂时的,没有人会一直年轻。大部分人随着经验增加,收入提高,就会跳出最低的20%的收入组,但是仍有一小部分(大约5%)停滞在此收入组中,然而我们不能随便就此认定这种不同寻常的命运与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无关。
就像罗尔斯所言,除非有助于社会底层,否则从道德角度看,一切皆不可为。50这等同于为了那些秉持非生产性生活方式的人而否决任何进步。一些结论或许在宿命论的世界里是合理的,但并不适合个体有选择权的世界。人们的选择受过去的社会条件影响,并不意味着不会受当前行为的回报或惩罚的影响,因此,我们社会对那些非生产性行为进行不加评判的补助最终会影响人们的选择。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考察了世界各地的人们——不论是国家间,还是一国内部——的收入与财富差异,探寻背后的原因,其实也是在寻找生产率差异的根源。有些人更关心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却忽略它们的生产过程。这样一来,再分配主义者就不必面对这一问题:收入不平等的结果是否与经济生产效率上的不平等相对应?
再分配主义者努力鼓吹的观点是,鉴于个体有许多意外横财或意外损失,目前的许多回报是不公平的。其中的核心是“出身的偶然性”。简言之,根据“正义比效率更重要” 的罗尔斯主义原则,再分配主义者评判行为,偏向于美德标准更甚于生产率标准,某些情形下甚至可以不考虑生产率。
我们同样能应用“社会正义”支持者的标准来进行讨论。假想一个人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父母贫穷,而且酗酒、不负责任、不管不顾或虐待子女。这种成长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会让人痛苦不堪,但这个人会努力成为一个正派、辛勤工作的人,学门手艺如木工来养活自己和家人,让家人的境遇远远好于自己童年时的环境。倘能做到,也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
假想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出生的人,有爱他和关心他的父母,家境小康或富有,所处的社会地位带给他成长优势,包括接受水平更高的私立教育和更广的文化熏陶。这样一个人如果成了脑外科医生当然值得称赞,但无论如何并不比木匠的成就更值得赞美。
在一个基于功绩给予回报的世界里,脑外科医生的收入没有理由比木匠高。但在“生产率更重要的”的世界里,关键不再是个体的相对功绩。相对于基于功绩的“社会正义”, 对特定的工薪族而言,更重要的是他们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带给人们的福利水平。将生产纳入讨论,结果将有很大的不同。某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多选择也许看起来是非正义的,但关键问题变成了脑外科手术与木工哪个更重要,以及如何激励能力较强(不论能力高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的)的年轻人,让他们在众多选项中愿意接受时间更久也更具挑战性的脑外科医生训练。
我们不能只重视特定个体和群体在收入上的相对经济命运,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个体和群体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收入再分配主义者总是将矛头对准这些个体和群体,但是他们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使社会其他成员受益。
把消费者的命运看作“效率”问题,又把那些提供产品和服务获取收入的人的命运看作“社会正义”问题。然后就像罗尔斯那样视“社会正义”在绝对意义上比“效率”更重要51,实质是没有区分这两个有差异的事物。倘若收入再分配的方式降低了效率,两者的区别便关联了起来,而比起“社会正义”给一些人带来的经济所得,作为消费者那一群人的损失被随意地认为不那么重要。但倘若人们遭受了不应遭受的损失都算不上非正义,那怎样才算呢?人们作为消费者遭受不应遭受的损失为何在道德上不同于人们作为收入者遭受不应遭受的损失?这一点实在匪夷所思。
“解决方案”
知识界与政府联合起来,用强力迫使数百万人撤销达成的经济交易合约,然而只有当事人才能熟知他们所处的环境及可替代的选择,身在事外的知识分子或政府官员不可能了解。这种行为的逻辑基础一定会引发疑问。此外,倘若这些数以百万计的人并不认同罗尔斯“正义比效率更重要”的观念,又当如何?事实上,如罗尔斯所言,对于任何两个有价值的事物,一个事物不可能在绝对价值上比另一个更有价值。52一颗钻石或许比一便士价值更高,但只要便士够多,它们的价值一样可以超过钻石。
在挂满常春藤的大学里,无忧无虑的学术界人士会选择与他们的偏见相匹配的统计模式和收入数据。但不能就此认为深陷贫穷“陷阱”的穷人——在第三世界中属于极度贫穷 ——欢迎亿万富翁投资者是错误的。亿万富翁的投资使他们自己更富有,这一点也许会让身处校园和编辑办公室的人感到不适,但也正是这些投资者投资建厂,才给穷人提供了工作岗位,使他们可以给家庭提供以前负担不起的东西。③
相比更繁荣且更有能力救助穷人的社会,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正义”论的支持者或许更偏好一个从统计上看起来更平等的社会。当然,这些人坚持这种观点是他们的权利,不过其他人包括低收入者也有权利偏好一个更繁荣的社会。倘若其他国家的穷人跟美国知识分子一样厌恶美国的不平等程度,那么就无法解释长久以来全世界各地的贫穷移民大规模移民美国。
以“社会正义”的名义宣称更道德、更平等或更有人道主义,因而主张无数的人类同胞被迫去接受安排给他们的生活,以此取悦少数知识分子或政治家。这种想法本身就很可笑,而且令人震惊。
基于人们的生产率而非功德给予他们回报,原因之一是生产率更容易测度。在市场经济中,产品价值高低由买者和使用者来评价,情况更是如此。很少有人能了解他人的价值, 因为他们没有“穿着他人的鞋子走一走”。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我们不用帮助那些出生在不幸环境中的人拓展选择机会,但这样一来,他们提升自我生产率的选项就更有限了。在美国的历史上,人们从来没有对这类人不管不顾。数百年来,美国社会中一直有大量志愿性慈善事业。很多私人慈善事业创立学校、图书馆、奖学金、大学、基金、医院和其他民间机构,在这方面,美国一直如此,并且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国家,这些机构通常是由政府或宗教组织建立的。
做到这些不仅需要金钱,还需要人们不断将时间投入公民事业,其中一些项目旨在增加不幸者的选择。美国内战后,数以千计的白人从北方来到南方,在慈善人士创立的私人学校里教授新解放奴隶的子女,这是一个典型例子。
这些教师通常是年轻女性,她们勇敢面对恶劣的条件。这其中既包括南方白人社会的敌意——她们经常受到排斥甚至威胁,还要面对众多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黑人学生。奴隶经历和南方那种“教育是高人一等的特权”的文化阻碍了这些学生的发展。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称这些北方来的白人志愿者从事的工作是“美国历史上最美好的事”53。
许多人不考虑一般意义上的生产率,不论是经济方面的还是社会动机方面的。他们当然也会忽视类似上述北方白人的慈善活动。但这样出自公德心的自发行为不能被认为理所 应当,它既非自然而然的,也不是总会发生。经济生产活动经常被视作理所当然,实际上它们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有巨大的差异,给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同样,公益活动的差异也很大,它们在世界各地发生的概率不一样,而且在整个西方文明中的活跃程度也不同。
19世纪,法国人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访问美国,美国人的自发慈善活动之广泛令他感到震惊。这一点在他的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有详细记录。54 20世纪中期,著名的美国学者爱德华·C.班菲尔德(Edward C. Banfield) 曾在意大利山村中停留,却发现那里的人们对慈善活动并不热心,也没有开展慈善活动。 在那里,许多人认为“为公众着想是不明智的”,也没有人会“伸手去帮助一个正在搬运重东西到山顶孤儿院去的修女”,即便当地的修道院已经破败得摇摇欲坠,“也没有哪个泥瓦工会愿意拿出一天时间去做些修补工作”。55
与此类似,20世纪一项对俄罗斯社会的研究发现,相比于美国,俄罗斯人极少有公民责任心,一般性的自发社会活动也不多。一项针对60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研究发现, “俄罗斯在体育类和娱乐类的排名最高,从倒数后几位上升到第9位”。在该类别中, “被调查的成年人中有将近4%说他们加入了一个体育俱乐部或其他体育组织”。但只有2% 的人表示它们参与了帮助他人的志愿性社会福利活动。
该研究发现,美国人参加“体育类和社会福利类组织的比例比俄罗斯大约高10倍,参加环境类、宗教类和职业类组织的比例高20倍,参与文化教育类和妇女组织的比例高30倍, 参与人权组织的比例大约高50倍”。56
人们尝试提高那些生于相对不幸环境中的人们的教育和经济水平,但这样的努力通常会受限于社会对他们的接受度。他们成长的文化没有给他们提供最大化利用潜在机会所需要的期望、习惯或纪律性。落后群体的领导者经常会阻碍该群体的发展,因为他们完全有动力推动人们形成这样的愿景,即该群体的问题主要是由其他群体犯下的罪恶造成的,倘若不是全部的话。这样一来,他们还有什么激励去努力尝试改变自我呢?
**这种领导模式存在于每一个有人类居住的大陆。因此除非各地有非常例外的领导者出现,我们没有理由期待美国或其他国家会是另一个模式。18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大卫·休谟曾呼吁他的苏格兰同胞学英语,这是因为他并非族群领袖。当你想帮人们时,你会告诉他们事实。当你想帮自己时,你告诉人们的是他们想听的。那些族群领袖通常讲给追随者听的都是后者想听的。
一些人一直在推动这样的愿景,即黑人的落后、与白人的差距或不平等是由他人的过错造成的。并认为一旦民权法案和政策对其他人施加约束,所有这些落后、差距或不平等都会消失。他们实际上是被困在了这样的结论中。但20世纪60年代民权革命兴起,他们期望的结果并没有发生。黑人在全美或地方的政治代表人物明显地增加了,但并没有降低相应的经济不平等程度。经济进步一直有,但黑人摆脱贫困的速度还比不上20世纪60年代民权革命兴起之前的那些年。57
即便如此,抓着这一愿景不放的人仍然宣称即使缺乏证据支持“黑人持续的落后、差距或不平等是因为他人的所作所为造成的”,这也只不过表明“恶毒的”或“制度化的” 种族主义被“恶魔式”的聪明所掩盖。如果没有实际的证据来证明一个需要实际证据才能证明的命题时,这实质上就是一种专断的论证,“不管怎样,都是我赢”。但是,这些人被迫孤注一掷,在他们论争的前提条件中,基因决定论若隐若现。因此这些人的观点激烈却很勉强且缺乏说服力,只能提出别的替代性解释。
相对于流行的民权愿景,更现实的前提假设能使这些辩护者免于画地为牢,抱着这一不可靠的结论不放。东欧人和西欧人的经济差距超过非洲裔美国人和白人的差距。58虽然西欧人没有阻碍东欧的经济崛起,但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百年。那些期望黑人在几个世纪内就能赶上白人的人,很明显在他们的测算中漏掉了很多因素。
考虑到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境遇,他们过去的经历不需要深奥难懂的道歉,也不需要将责任推给他人。正如20世纪早期一位美国南方白人学者观察所言:“面对更大的障碍, 没有种族会前进一步。”一个“文化传承被野蛮割裂”的民族,在三代内就会变成“与西方文化中的农民阶层相似的一群人”。在那个年代,黑人停止进步“或许是源于不可避免的身体特征”造成的限制,即基于肤色的社会隔离。尽管“在文化机遇上受限,被种族偏见的火障团团包围,黑人拥有了部分土地的所有权,在一些行业取得了高级职位,在文科和理科中都取得的一些成功。这些成就对任何民族而言都是了不起的”。59
在他所言的年代里,大多数黑人成人只接受了小学程度的教育,并且是在比较糟糕的南方学校里接受的教育。在奴隶制废除后的第一个一百年里,黑人实现了巨大的进步,但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下层黑人的行为却经历了惊人的退步,这种退步随后蔓延到其他黑人阶层。人们不仅不愿意承认这种退步,更不愿意去应对。这就增加了黑人进一步缩小与白人经济差距的难度。
财富的国际差异
全世界各国的地理、文化、历史、政治体制、宗教信仰以及人口结构差异非常大,倘若所有国家有相近的收入或财富,这本身就是奇迹。当然,当前的现状也绝非是宿命的, 过去那些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今却处在人类成就与繁荣的最前沿,它们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来改变命运。18世纪的苏格兰、19世纪的日本以及20世纪的新加坡和韩国的崛起,都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可以做的,以及如何做。
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的崛起确实鼓舞人心,并且无一例外,他们的崛起都不是依靠所谓的“外国援助”带来的国家间财富转移。他们的崛起也不是因为外来者——外国政府、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各类专家——帮助他们进行“国家建设”。虽然很多人将某些国家的贫穷归咎于其他国家或外国投资者对这些国家的剥削,但很难找到有哪些国家是通过摆脱殖民负担或没收外国投资者的财产而从贫穷走向富裕的。事实上,有很多相反的例子却反映了这样做所遭受的失败或带来的反生产性后果。60
凭借压迫或暴力活动驱逐各类被描绘成“剥削者”或“寄生虫”的少数群体,并因此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国家更少见。驱逐少数群体的例子很多,如东欧的犹太人、缅甸的印度人、东非的亚洲人和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各类少数群体。
那些驱逐少数群体的国家往往经济会变得更糟糕,而接纳这些少数群体的国家则经济会变得更好。美国就受益于来自欧洲的数百万犹太人,他们的到来为各行各业提供了更多劳动力,并且这些移民中还有许多世界级科学家,在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的科学家中,很多都是犹太人,而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因原子弹的诞生得到了稳固。
历史上有很多征服他国的国家,如大蒙古国、西班牙、奥斯曼帝国等,他们的后代并没有从祖先的历史性功勋中获得经济上荣耀。有一些征服行动给征服者后代带来了繁荣昌盛,但发起征服的国家通常已经很富有了,例如英国征服澳大利亚和北美大部分地区,并定居于此,他们的后代在两地都替代了土著人口。西班牙在西半球进行了大规模的征服侵略,拉丁美洲各国很少能像英国前殖民地北美或澳大利亚那样繁荣,虽然拉丁美洲国家的土地更肥沃,自然资源也更丰富。
这些差异如此之大的国家如果有什么共通之处,那就是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一国内部的不同族群看出这一点。
比如,阿根廷被称作“世界上资源禀赋最好的国家之一”,土壤“非常肥沃”,植物的根可以伸入土壤15英尺而无岩石阻碍。61并且与其他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不同,阿根廷的人口大部分都有欧洲血统。但是,人口大多具有撒哈拉以南非洲血统的巴巴多斯——该岛人口起源于比欧洲更贫穷的地区——人均GDP却比阿根廷高出40%。62
虽然巴巴多斯人作为奴隶抵达西半球,而西班牙人是西半球的征服者,但巴巴多斯人吸收了英国文化,他们的寿命也比他们的来源地撒哈拉以南非洲居民要长。英国文化与西班牙文化有很大区别,对于工作、教育、企业家精神和其他文化因素的价值,英国文化大力提倡,而西班牙文化则非常蔑视。阿根廷国内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更加印证了这一结论, 在西半球承袭了西班牙文化的人群的经济生产率比西欧地区要低,而西班牙在整个西欧国家也属于长期相对贫穷的国家。
从西班牙以外的欧洲其他地区到阿根廷的移民,虽然在刚抵达时很穷,但经过努力在经济上也比阿根廷本地人更成功。意大利移民更是如此,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早期移民中, 意大利移民人数最多。早在1864年,意大利移民占阿根廷全部移民的40%,半个世纪以后的1914年,这一比例仍然接近40%。63
阿根廷的意大利人与阿根廷本地人在两个方面差异非常明显:一是意大利移民愿意从事最苦的工作;二是意大利移民虽然收入不高却愿意储蓄。阿根廷农业对于来自意大利的季节性移民有很大需求,而19世纪该产业的大规模扩张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这些意大利农工。64除了这些随季节来去而被称作“燕子”和“飞燕”的农工,也有一些意大利农民定居阿根廷。后者开始只是雇工,慢慢经过多年积攒成为佃农并最终成为地主。65
虽然阿根廷土壤肥沃,却一直进口小麦。直到外国农民,特别是意大利农民以及来自俄罗斯的德国人到来,阿根廷才成为世界主要的小麦出口国之一。66“阿根廷的土壤适合种植小麦”是事实,但这一事实因为阿根廷有了能够成功种植小麦的农民群体才变得有意义。我们再次看到,地理并非是宿命的。
就像在农业中一样,阿根廷本地人在城市的表现也不如移民。1914年,占总人口30%左右的外国移民掌握阿根廷72%的商业,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一比例更是高达82%。 67在该城市中,意大利企业家主导着除啤酒之外的酒精饮料的生产,而德国人则主导了啤酒酿造。68
阿根廷人以“不爱储蓄”闻名于世,被称为“世界上最挥霍无度的一群人”。69 1887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银行的储户中,意大利市民是阿根廷市民的两倍。70在那个年代, 大多数意大利移民是劳动者,阿根廷大多数泥工、水手、贸易商、建筑师、进口商、工程师以及餐馆旅店所有者主要是意大利人。71
【注:储蓄而不是消费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啊~】
阿根廷政府自身也意识到了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移民的差别,努力吸引西班牙以外地区的移民。起初,他们有意识地吸引来自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移民,但很不成功。 然后转向欢迎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移民,但更偏爱北方意大利人和西班牙的巴斯克人, 两者与南方意大利人或西班牙其他地区的文化差异很大,例如巴斯克人以“节俭和勤奋工作”著称。72阿根廷政府也派代理人到欧洲去招揽德国人。73伏尔加河的德国人到阿根廷定居后,他们聚居的地区便成为阿根廷的小麦主产区。74
【注:节俭、勤奋工作确实是好品质~】
虽然阿根廷流行的是西班牙文化,但来自非西班牙文化的人们主导着该国经济,而阿根廷当地人则主导该国的政治机构。20世纪初,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甚至超过法国和德国。75但到了20世纪中期,灾难性的政治决策使阿根廷不再是经济处于世界前沿的国家。虽然阿根廷拥有肥沃的土壤和其他自然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也使其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但其政治文化毁掉了曾经辉煌的经济繁荣。政治上救世主式的政治煽动和阶级斗争式的语言与政策,在胡安·贝隆(Juan Perón)及其妻子 ——被人称作“非白领劳动者”女保护人——贝隆夫人身上都有所体现。他们只是经济上反生产性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模式在他们之前就开始了,在此之后又延续了很长时间。它消解了自然带给阿根廷的发展优势,也消解了移民、国际投资者和企业家这些外来者提供的人力资本。
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上依赖外来者,特别是那些创始国是非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国家。即使到了20世纪中叶,在巴西的大部分工业州,如圣保罗州、南里奥格兰德州、 圣卡塔琳娜州,大多数实业家都是近些年的欧洲移民或移民子女。在圣保罗州,“714家企业中有521家所有者属于此类”。在南里奥格兰德州和圣卡塔琳娜州,将近80%的产业由 类似特征的人开创。76其中,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尤其突出。在20世纪初的南里奥格兰德州, 金属家具、运动短裤、炉灶、纸、帽子、领带、皮革用品、肥皂、玻璃、火柴、啤酒、糖 果和四轮马车,所有这些产品都是德国人生产的。同样,铸造厂和木器商店的所有者也是德国人。77
不只是工业,巴西的农业移民也主要来自伊比利亚半岛之外的地方。和阿根廷政府一样,巴西政府也有意识地吸引欧洲各地的德国人78,因为德国移民愿意从事垦荒这样的重体力活,他们不像巴西那些来自葡萄牙文化的人群或阿根廷那些来自西班牙文化的人群那样鄙视此类工作。圣保罗州曾向移民到该州的意大利农民提供补贴。79智利和巴拉圭政府为了开垦野外的处女地,也有意寻找伊比利亚半岛以外的欧洲移民,这些移民既工作勤恳,也能接受野外严酷的生存条件。80
简言之,这些政府早就认识到不同人群在工作习惯、技能和价值等方面存在文化差异。不论是农业、工业还是商业,文化是发展国民经济所必需的。但到了今天,承认文化差异却变成了禁忌。用法国知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话说,正是移民“创造了现代巴西、阿根廷和智利”。81
并非所有移民都来自欧洲。日本移民在巴西和秘鲁经济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20世纪30年代初,巴西圣保罗州的日本人仅占全州人口的2%~3%,他们拥有的土地还不到2%,却生产了该州将近30%的农业产品,包括46%的棉花、57%的蚕丝和75%的茶叶,还有很大一部分的香蕉也是由日本人种植的。82
在南美的秘鲁,日本移民人口较少,但他们对经济的贡献却远远超出其人口比例。日本人移民秘鲁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们最早是当农工,工作环境恶劣,死亡率很高。 83随后很快就搬到了城市社区,从事的职业包括家庭仆人,慢慢开始成为小企业主。84最终,秘鲁首都利马四分之三的理发店和200家杂货店是日本人开的。即使是做农工,日本人的工作习惯也使得他们比秘鲁农工更受欢迎,所得的报酬也更高。85
日本人赢得了勤恳工作、可信赖、很诚信的名声。86而且他们比秘鲁人更关心子女的教育。1876年,秘鲁的文盲率是79%,在几代人之后下降了许多,但到1940年,仍有58%的人口是文盲。87那个年代的秘鲁制造业企业通常由外国人或新移民控制。
就像其他地方其他时代的成功少数人群一样,秘鲁的日本人也遭到当地人的憎恨。秘鲁人通过社论批评和抵制日本人的企业来表达憎恨。由于日本人的商品价格更低,这些抵制活动失败了。88但通过政治手段反对日本人则达到了效果。这些手段包括通过法律要求企业雇员中秘鲁人比例不低于80%89,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严格限制日本向秘鲁移民。9 0
在智利,外来者总体上在该国经济发展中起着远超人口比例的作用。晚至20世纪中期,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的大部分工业企业由移民或移民的子女所有。91这种模式在拉丁美洲司空见惯,在各国商业和工业巨头中,非西班牙裔、非葡萄牙裔的移民及其子女所占比例非常高,有时甚至是绝对优势比例。92
不论是在欧洲还是西半球,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上层社会有一种对工商业的蔑视,与此并行的是底层社会对体力活和繁重工作的厌恶。这种态度并不仅仅是懒惰。一位学者在一本书里写到17世纪的西班牙,就曾描述西班牙人的这种特征,即“以懒惰为荣”,反映出这种文化在骨子里将体力活贴上“耻辱”的标签,人人都很厌恶这种工作。93
数百年后,巴拉圭的日本农民在聚居地不停歇地辛勤工作,巴拉圭本地人对日本人的这种干劲很困惑。94同样,洪都拉斯的农民抱怨说,让他们跟德国农民竞争是不公平的, 后者被认为工作太过努力了。95
在世界舞台上,有许多国家的人不仅无法达到别国的生产率标准,而且断然拒绝、憎恨并且限制那些生产率高的人,用谴责国内外其他人的剥削来解释他们自身的落后。这不只发生在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学者引领并发展了所谓的“依附理论”,用南美的落后谴责北美以及其他国家。然而亚洲国家向国际贸易、投资者和技术开放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功,也销蚀了拉丁美洲“依附理论”的基础。但拉丁美洲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数代人自我放纵、不愿奋进。
当我们考虑文化或其他因素可能造成了特定结果时,不能忽视时间。放弃“依附理论”会使得更大的经济进步成为可能,但该理论多年来带给经济增长的障碍已无法消除。同样,当某一个国家的人口大多仍是文盲,而其他国家已经在数代人或数百年里普及了教育时, 教育在该国的普及当然会使该国受益,但并不会使之立刻追赶上那些教育普及成为常态的国家。
在另一个意义上,时间也很重要。长久以来人们观察到,相对于原产国,一种文化移植到其他国家很大程度上会保持原样。因此,魁北克的法语和墨西哥的西班牙语中有许多单词和语句在法国和西班牙都属于古老的语言。据说,拉丁美洲传承自西班牙的反生产观念在西班牙本国已经开始转变,但这种转变却鲜见于拉丁美洲。96
英国的前殖民地,即那些由英国移民创立的国家,总体上比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在经济上更繁荣,这一事实无可辩驳。这并非因为大英帝国在选择定居点上做出了更好的选择,因为西班牙帝国创立更早,他们在殖民地的选择上也领先一步。早在16世纪,西班牙人已经在北美和南美攻占了领土并攻击当地人。直到17世纪,英国才在詹姆斯敦建立了美洲的第一块永久殖民地。
直面事实及未来
财富、贫穷与政治涉及很多社会和经济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最紧要的不一定是开出特定的政策“处方”。人们也已经提出许多蓝图用来建立乌托邦,相比之下,我们缺少的是对当前问题及未来选择进行理性思考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中最重要的是真正的事实。无论我们找寻的目的地是什么——可以是直白的,也可以是描绘出来的——出发的起点总是当下。这意味着为了向我们的目的地前进,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必定是与我们当前相关的事实。
如果我们的目的地是夏威夷,那么首先要知道我们在夏威夷的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否则,我们可能会一直沿着错误的方向前行。如果我们的目的地不是地理位置上的,而是比喻性或社会性的目标,也仍要遵从同样的原则。例如,如果我们期望加快非洲裔美国人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进步,就应当知晓今天这一群体的现状如何,而不是我们期待他们是什么样,也不是部分黑人自己认为的或使其他人相信的他们当前的状况。前提如果错了,结论也很少会正确。
那么,阻碍我们知晓事实的障碍有哪些呢?
不幸的是,障碍太多,太明显。它们包括铁证如山却不能言说的东西,可以公之于众却没有证据支持的东西,以及无视任何相反的证据。在大学校园里,这些障碍最明显不过。 老师或学生倘若公开谈论关于少数族群那些令人不快的真相,他就会遭到反对,被认为是社会渣滓,受到校园言论规则的惩罚,甚至遭受暴力攻击和威胁。
与此同时,有些事情不论多么虚假,都是可言说的。而谈论这些虚伪的东西不会受到批判,也不会因此名声败坏。
不幸的是,在太多场合,不论是学术界、媒体还是政府,我们听到的大多是虚假且具有误导性的武断假定。其中最流行的一种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其他人的恶毒行为造成了国家间或一国内部不同群体间的经济差距。这一论断隐含的假定就是,如果不是他人的恶毒,各个群体的经济结果将是平等的。但全世界各地的地理、人口和文化以及其他因素都会影响经济结果,平等是不可能的。更不必说,在个人努力可以被客观度量的领域,如体育、国际象棋、拼写大赛等,个人的成绩在分布上也是高度有偏的。
影响个体经济效率的因素众多,人们具备这些因素的可能性也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意义上的机会均等与实现某项目标的机遇同等也是非常不同的。但这一差异经常被忽视或混为一谈。
即使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这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曾 说过:“考察机会均等的方式之一,是看儿童的人生际遇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教育和 收入。”更具体地说,他问道:“一个出生在父母教育程度不高的家庭的儿童,能够接受 良好教育并成为中产阶级的可能性,是否同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父母有大学文凭的孩子 一样高?”他说,“拉美裔美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工作报酬仍低于白人,妇女的报酬也 低于男人”,并以此作为机会不均等的证据。根据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说法,“美国人正逐 渐意识到,他们所珍视的关于社会和经济流动性的故事成了一个神话”。97
【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确实是典型的左派经济学家~】
混淆“机会均等”与“成功可能性均等”会造成什么后果?此时人们不会考虑“是否某些人比其他人能更好地利用机会”的问题,这种处理很巧妙。当纽约三所老牌公立高中 ——史岱文森高中、布朗克斯科学高中以及布鲁克林工程高中——的亚洲学生与白人学生的比例超过2∶1时98,我们能说白人没有获得同等机会吗?
我们知晓来自福建省的华人的收入和教育水平都很低,这样我们还能说亚洲人的收入和教育水平超过白人吗?当我们知晓富人区榭柯高地的黑人医生和律师的子女忽视学习功课,我们还能将“机会均等”与“同等的可能性”等同起来吗?99
语言很重要。有时运用诡辩式的语言,能够将缺乏证据的事讲得有理有据。失败群体之所以失败,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外部障碍——机会更少?又有多大程度是因为他们内在的知识、纪律性、价值观和其他能够影响他们人生机会的因素不足呢?对于探寻真相的人而言,这一问题十分关键,但对于只想在意识形态上取胜的人而言,这一问题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如果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偏爱制造“人生机会”的话题,那是他的权力。但宣称他已经驳倒了其他人关于社会流动性的信念,并宣称这种信念只是一种“神话”,实质上是将他自己的社会流动性观念强加给他人。而且把黑人与白人或男性女性之间的收入差距视为证据,这就更让人困惑。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这种差距背后的根源是外部的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
然而,已有的众多实证研究发现,黑人的工作能力逊于白人。同样,男性和女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不同。除了其他有重要影响的差别外,最简单的事实是,女性年工作小时数和持续工作年限都更短。100
早在1971年,虽然女性群体的收入少于男性,但倘若单身女性从高中毕业一直工作到30岁,她们挣的还要略多于工作年限相同的男性。101在1972—1973学年,当时黑人学者的收入整体上低于白人,但从高水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且发表相同数量文章的黑人收入却高于同等条件的白人学者。102
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论证方式并非个案。不论是讨论不那么成功的社会成员,还是讨论成功的社会成员,重新界定概念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讨论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武器。当人们讨论较成功的群体时,“成就”概念被偷换成“特权”。例如,有人指出,收入统计数据显示,“根据年收入、教育水平和职业声望判断,爱尔兰天主教徒族群在美国属于第二大特权族群,这一点毫无争议”,而犹太人是“最具有特权的种族”。103
我们要看到,19世纪爱尔兰和犹太移民抵达美国时,他们在移民中属于极端贫穷的一群人,生活环境之恶劣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由此可见,这些判断是如何可笑。
一个世纪后,爱尔兰人和犹太人在困苦中逐渐富裕。这是一种成就,而不是什么特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的境遇非常糟糕,曾有雇主在招工时发出告示“此岗位不招爱尔兰人”,哈佛大学和其他老牌学府招录的犹太学生也有名额限制,而且任命的犹太人教授更少,甚至没有,这些限制却反衬出他们的非凡成就。但如今一些人想玩弄文字游戏, 称他们是“有特权的人”104,否定他们的成就。同样,黑人中产阶级的祖先来到美国时, 也不可能是医生、律师或教师,但他们也被描述为“有特权的人”。
不只是政客或记者,严肃学术刊物上的文章在讨论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族群差异时,也同样喜欢玩弄文字游戏。例如,由于政府命令,马来西亚公共机构和私人组织普遍更偏向马来人,但马来人依然被称作“没有特权的人”105,而非马来人被视作“有特权”的人106。类似地,在多伦多,日本裔加拿大人由于收入更高,于是被描述成“有特权的人” 107。这种说法忽略了历史上加拿大曾经有过反日本人的歧视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设立了日裔集中营,反日运动达到顶点,而日裔加拿大人比日裔美国人遭受的拘役更久。108
总之,在讨论某些族群取得的成就时,用“特权”替换“成就”磨灭了他们长久艰辛的奋斗。尽管我们都知道,特权指的是一种事先的条件,而成就指的是一种事后状态。更重要的是,在讨论族群间的经济不平等时,这样的技巧避开了对行为和生产效率的讨论。 其他技巧包括将任何关于特定群体的负面信息归为“陈词滥调”而不予考虑。这种语言诡辩让一些词汇“面目全非”,进而无法传递再分配主义者要极力规避的不受他们欢迎的事实,也就成了探寻真相的障碍。
除此之外,这些观点聚焦于随成就而来的回报,却无视他们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带给他人的福利,也无视了人们愿意花钱购买这些福利。正如在其他情形中一样,当再分配主义者讨论“生产效率决定收入分配”时,他们运用文字游戏对生产效率问题避而不谈。看起来就像重要的只是A和B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不必考虑A和B各自成就带给C、D、E以及其他人的福利。
仅仅关注成就不同的人在福利上的差异,就会看不到这些人的成就带给整个社会的福利。在史前时代,不论是谁发明了轮子或第一个想出生火的办法,他就比其他人领先一步, 但最重要的是,这些事物极大地增进了尚处于“婴儿期”的人类的人力资本。或许全世界每个人都在同一时间取得同样的进步会更棒,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是,人类只有真实地取得了这些根本性的进步,才能迈向文明社会。
今天,一些父母养育子女的方式容易培养出医生、科学家或工程师,而另一些儿童成长的方式使得他们更容易成为领取政府福利的人或罪犯。两者的差别不仅限于这两类儿童在未来的发展优势,还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福利。一些学者谴责学校的录取政策过于看重申请者的学业成绩,在他们看来,这简直就是奖励那些“拥有特权的人”。就像尼日利亚的种族活跃分子谴责的“技能的专横”109,不同录取政策对社会的影响在人们的讨论中消失得毫无踪影。
从某种意义上说,“技能的专横”是存在的,但它的存在与任何一个特定的组织或社会都不相关,因为它内在的根源不受人控制。例如,医疗技术影响着数百万人的生死,这就是我们无可逃避的现实或者说“专横”。一个特定的组织或社会所能做的不过是要么承认这一技能的价值,要么使技能屈从于人们的社会偏见或政治权宜之计。技能带来的福利, 不止局限于技能拥有者,还包括缺乏这些技能的人。纽约精英高中和精英学院培养的毕业生发明的骨髓灰质炎疫苗,对全世界不同收入阶层、种族、肤色、宗教信仰和国家的民众都是福音。
人们总是惊讶于不同个体、族群或国家所获得回报的巨大差距,但很少追问获得丰厚回报的人所生产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是不是也有很大的不同。再分配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并无多少建树。因为很少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人就更少了。 这再次说明,生产问题被遗落在模糊的背景里,就像不管怎样都会如此一样。
有些研究针对的是那些超级富豪,如约翰·D.罗斯柴尔德,这类研究或许会充满对他们“贪婪”的指责。但使用“贪婪”这种词汇来描述罗斯柴尔德人格的人很少会提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罗斯柴尔德究竟给他人提供了什么,以至于让那么多人将他们微薄的钱财付给他,使他能够积累巨额财富?
在此类情形中,“贪婪”一词经常被提到,但它什么也解释不了,除非你相信只要对金钱贪得无厌,别人就会付钱给你。“贪婪”虽然在因果关系上毫无解释力,但却流行于知识界,一句老话传递了根本的事实:“如果愿望都能实现,乞丐早就发财了。”无论一个人是否真的具有“贪婪”的品性,如果他仅仅只有愿望,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人会给这些贪婪者钱财来满足他们的愿望。
而且财富多寡并非贪婪的“气压计”。一个小混混为了一丁点儿钱抢劫一间小店,并杀人灭口,他抢的钱还比不上一名工程师或外科医生诚实工作一个月的收入。在这个案例中,贪婪的是那个小混混。
就约翰·D.洛克菲勒而言,其财富积累开始于19世纪,通过在生产和运输煤油上的创新发明,极大地降低了生产和运输成本。110即便到今天,我们仍用桶(barrel)作为度量石油的单位,而正是洛克菲勒通过铁路罐车取代了原来的用桶装运石油的方式,节省了运输成本。
这一变革发生之时,电灯泡尚未问世,有一句古老的谚语是这样讲的:“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许多劳动阶层的人晚上用不起蜡烛或燃油,在夜幕降临后别无选择只能上床睡觉。洛克菲勒改进生产和运输方式后,煤油成本极大地降低了,普通民众也能在黑夜中点起煤油灯,多享受几个小时的光明生活。
他们购买的是每年数百小时的额外光明,成百上千万人愿意为延长他们的生命而购买煤油,这毫不稀奇。
我们视今天世界的许多便利为理所当然,很难想象过去的人曾经是怎样生活的,也就很难体会那些里程碑式的进步如何让人们突破了时代的种种限制。
据估计,19世纪早期的大多数美国人在其一生中,活动范围不超过出生地为圆心的半径50英里内的区域。111铁路和汽车的出现大大扩展了人们的活动范围,特别是20世纪初亨利·福特批量生产汽车,显著降低了汽车的生产成本。从此汽车从富人才能拥有的奢侈品变成了大众也可以使用的代步工具。
==亨利·福特的发明提升了生产效率,进而扩展了数百万人的生活边界。而他由此积累的财富只是意外的副产品。为什么有人觉得有权干预这一过程,尽管他们对此毫无贡献? 为什么他们认为有权替他人做决策却不需要承担决策错误的代价?这是我们时代众多迷思之一。==
==从历史角度看,发明了一种新产品或使旧产品功能更好或价格更便宜,甚至有时仅是让旧产品既廉价又更好用,这些都能带来财富。不论是医生的医术,还是飞行员将数百人送到千里之外的驾驶技术,他们因技术获得的回报源于这些技术会改进人们的生活。掌握这些有价值的技艺,以便有能力从事这些工作或做其他事情,是一种有益他人的成就,而不是损人利己的“特权”。无论在语言上如何模糊它们之间的差异,两者在根本上是有区别的。==
再分配主义者或许要求提供证据,证明所有的财富或所有高收入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但这是将举证责任推给他人。他们应该让那些限制别人根据自己意愿自由生活,限制别人随心所欲地自由做出经济决策的人提供证据。说今天的知识阶层或政治家应当承继早先时代的那种“君权神授”,是毫无道理的。
市场经济没有不完美之处吗?当然有!所有事物都有缺陷,包括市场经济的替代物。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指出的:“对人类制度的研究总是在探寻最能忍受的不完美。”112
我们说这一切当然不是说应维持现状,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也不应维持现状。即使是保守主义领袖,从18世纪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到20世纪的米尔顿·弗里德曼,都在推动重大的社会变迁。④他们反对其中一些变革并不代表他们反对社会变迁的其他方面。但是,“变迁”这个词不是“自我放纵”的空头支票,更不是在一种观念下允许所有放纵行为。这一观念认为不平等是邪恶的,因此应站在天使的一边,对邪恶势力进行一场正义之战。他们没有考虑这种世界观是如何自我鼓吹的。
还有一种更危险的观念,认为人生的机遇是绝对不平等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给予政治家更多的对国家资源的控制权和更多的对我们个体生活的干预权。这种观点造成的历史令人警醒。英格兰和美国实施的扩张性福利政策带来了物质福利,也伴随着痛苦的社会退步,进而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危害。
最重要的是,无论要推动何种变革,首先必须了解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了解事实,不论事实是悦耳的还是刺耳的,因为“变迁”意味着进步。本书目标是至少让我们了解现状和事实。有的是人想要绘制政治蓝图,我们唯有期待政策是以现实世界的“硬事实”为基础,而不是用华丽的辞藻或偏见伪饰。
注释
1Alan Greenspan, 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New York:Penguin Press, 2007), p.95.
2P. T. Bauer, Equality, the Third World and Economic Delusion(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 niversity Press, 1981), p.23.
3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 erty(New York:Crown Business, 2012), pp.1—2.
4Darrel Hess, McKnight’s Physical Geography: A Landscap.Appreciation, eleventh edition(Upper Sad dle River, New Jersey:Pearson Education, 2014), p.200.
5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p.428.
6“Class an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Times, May 30, 2005, p.A14.
7E. J. Dionne, Jr., “Political Stupidity, U. S. Style”, Washington Post, July 29, 2010, p.A23.
8Peter Corning, The Fair Society: The Science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Pursuit of Social Justice(C 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p.ix.
9W. Michael Cox and Richard Alm, “By Our Own Bootstraps:Economic Opportunity & the Dynamics of I ncome Distribution”, Annual Report 1995,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p.8.
10Ibid.
11“Movin’ On Up”,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3, 2007, p.A24;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 y,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S. from 1996 to 2005”, November 13, 2007, p.9.
12Niels Veldhuis, et al., “The‘Poor’Are Getting Richer”, Fraser Forum, January/February 2013, p.25.
13Armine Yalnizyan, The Rise of Canada’s Richest 1%(Ottawa: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 ves, December 2010).
14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 y Press, 2014), p.252.
15Thomas A. Hirschl and Mark R. Rank, “The Social Dynamics of Economic Polarization: Exploring t he Life Course Probabilities of Top-Level Income Attain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4 Annual Meetings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Boston, May 1—4, 2014, p.8;Mark R. Rank, “Fr om Rags to Riches to Rags”, New York Times, April 20, 2014, Sunday Review, p.9.
16Thomas A. Hirschl and Mark R. Rank, “The Social Dynamics of Economic Polarization:Exploring th e Life Course Probabilities of Top-Level Income Attain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4 Annual M eetings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Boston, May 1—4, 2014, p.13.
17Paul Krugman, “Rich Man’s Recover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3, 2013, p.A25.
18U. 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S. from 1996 to 2005”, November 13, 2007, p.4. 19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253, 254.
20Ibid., pp.252, 301.
21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S. from 1996 to 2005”, November 13, 2007, pp.2, 4.
22Ibid., p.7.
23Ibid., pp.2, 4.
24Ibid., p.11.
25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he 400 Individual Income Tax Returns Reporting the Highest Adjusted Gross Incomes Each Year, 1992—2000”, Statistics of Income Bulletin, Spring 2003, Publication 113 6(Revised 6–03), p.7.
26Josep.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27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473, 507;Robert A. Wilson, “Personal E xemptions and Individual Income Tax Rates, 1913—2002”, Statistics of Income Bulletin, Spring 200 2, p.219.
28Eugene Robinson, “The Fight-Back Plan”,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0, 2011, p.A17.
29Carmen DeNavas-Walt and Robert W. Cleveland, “Money In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2001”, Curren t Population Reports, P60—218(Washington:U.S. Bureau of the Census, 2002), p.19.
30来自最新的人口调查。U. S. Census Bureau, “Table HINC–05. Percent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s, b y Selected Characteristics within Income Quintile and Top 5 Percent in 2010”, downloaded on Octob er 28, 2014:https://www.census.gov/hhes/www/cpstables/032011/hhinc/new05_000.htm。
31Charles Murray, Human Accomplishment: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800 B. C. to 1950(New York:Harper Collins, 2003), p.298.
32Ibid., pp.304, 305.
33Ibid., p.98.
34Ibid., pp.97—100.
35James Corrigan, “Woods in the Mood to End His Major Drought”, Daily Telegraph(London), Augus t 5, 2013, pp.16—17.
36Charles Murray, Human Accomplishment, p.102.
37John Powers, “Kenya’s Domination in Marathons Has Raised the Level of Running Excellence, and the Rest of the Field Is Still Having a Hard Time Catching Up”, Boston Globe, April 12, 2013, p.C
38Josep.White, “A 1st in 52 Years:Co-champ.at the Spelling Bee”, The Associated Press, May 30,
39Sports Illustrated Almanac 2013(New York:Sports Illustrated Books, 2012), pp.69, 78.
40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lmanac 2014—2015, August 22, 2014, p.45.
41Ibid.
42U. S. News & World Report, America’s Best Colleges, 2010 edition(Washington:U. S. News & Worl d Report, 2009), pp.137, 140, 191.
43Mohamed Suffian bin Hashim, “Problems and Issues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Problems and Issues, edited by Yip Yat Hoong(S ingapore:Regional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1973), Table 8, pp.70—71.
44Previous lists of statistical disparities in outcomes have appeared in such previous books of mi ne as 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 Self-Congratulation as a Basis for Social Policy(New York:Basi c Books, 1995), pp.35—37 and 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 second edition(New York:Basic Books, 2 012), pp.116—119.Isolated examples have appeared in Conquests and Cultures: An International His tory(New York:Basic Books, 1998), pp.125, 210, 217;Migrations and Cultures: A World View(New York:Basic Books, 1996), pp.4, 17, 31, 57, 123, 130, 135, 152, 154, 157, 176, 179, 193, 196, 211, 265, 277, 278, 289, 297, 298, 300, 320, 345—346, 353—354, 355, 358, 366, 372—373.
45Thomas A. Hirschl and Mark R. Rank, "The Social Dynamics of Economic Polarization: Exploring th e Life Course Probabilities of Top-Level Income Attainment, “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4 Annual Meetings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Boston, May 1–4, 2014, p.13.
46Alan Reynolds, Income and Wealth(Westport, 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 2006), pp.27—28.
47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7
48Ibid., p.74.
49Ibid., pp.79—80.
50Ibid., pp.75—78.
51Ibid., pp.79—80, 82—83.
52Ibid., pp.4, 302, 303.
53James M. McPherson, The Abolitionist Legacy: From Reconstruction to the NAACP(Princeton: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98.
54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ited by J.P. Mayer and Max Lerner(New York:Harp er & Row, 1966), p.485.
55Edward C. 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58), pp. 19, 20, 76. 56Nicholas Eberstadt, Russia’s Peacetime Demographic Crisis: Dimensions, Causes, Implications (S eattl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0), p.259.
57Stephan Thernstrom and Abigail Thernstrom, America in Black and White: One Nation, Indivisible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1997), pp.233—234.
58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2013(New York:World Almanac Books, 2013), pp.748, 770, 7 71, 796, 806, 818, 821, 832, 839, 846;U.S. Census Bureau, “S0201:Selected Population Prof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3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1-Year Estimates, downloaded from the Census web site on November 10, 2014:http://factfinder2.census.gov/faces/tableservices/jsf/pages/productvie w.xhtml?pid=ACS_13_1YR_S0201&prodType=table
59Rupert B. Vance, Human Geography of the South: A Study in Regional Resources and Human Adequacy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2), p.463.
60比如见P. T. Bauer, Equality, the Third World and Economic Delusion, Chapters 5, 6, 7;William Ea sterly, 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New York:Penguin Press, 2006)。
61Lawrence E. Harrison, 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 The Latin American Case(Cambridge, M assachusetts: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p.103.
62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2014(New York:World Almanac Books, 2014), pp.750, 754.
63Robert F. Foerster, The Italian Emigration of Our Times(New York:Arno Press, 1969), p.236;Ca rl Solberg,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sm: Argentina and Chile, 1890—1914(Austin:University of Te xas Press, 1970), p.38.
64Robert F. Foerster, The Italian Emigration of Our Times, p.230.
65Ibid., p.243.
66Fred C. Koch, The Volga Germans: In Russia and the Americas, from 1763 to the Present(Universit 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227;Timothy J. Kloberdanz, “Plainsmen of Three Continents:Volga German Adaptation to Steppe, Prairie, and Pampa”, Ethnicity on the Great Plains, edited by Frederick C. Luebke(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0), pp.66—67. 67Carl Solberg,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sm, p.51.
68Robert F. Foerster, The Italian Emigration of Our Times, p.261.
69Mark Jefferson, Peopling the Argentine Pampa(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26), p.
70Carl Solberg,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sm, pp.49—50.
71Robert F. Foerster, The Italian Emigration of Our Times, pp.254—259.
72Carl E. Solberg, “Peopling the Prairies and the Pampas: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Argentine and Canadian Agrarian Development, 1870—1930”,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 s, Vol. 24, No. 2(May 1982), pp.136, 152;Gloria Totoricagüena, Basque Diaspora: Migration an Tr ansnational Identity(Reno:Center for Basque Studies, University of Nevada, 2005), pp.171, 180. 另外见Lawrence E. Harrison, The Pan-American Dream: Do Latin America’s Cultural Values Discourage True Partner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New York:Basic Books, 1997), p.151.
73Adam Giesinger, From Catherine to Krushchev: The Story of Russia’s Germans(Winnipeg, Manitoba, Canada:Adam Giesinger, 1974), p.229;Fred C. Koch, The Volga Germans, pp.222, 224.
74Fred C. Koch, The Volga Germans, pp.226, 227.
75“A Century of Decline”, The Economist, February 15, 2014, p.20.
76Seymour Martin Lipset,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Social Struct ures(New York:Basic Books, 1968), pp.90—91;Emilio Willems, “Brazil”, The Positive Contribut ion by Immigrants, edited by Oscar Handlin(Paris: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 ural Organization, 1955), p.133.
77Jean Roche, La Colonisation Allemande et le Rio Grande do Sul(Paris: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de L’Amérique Latine, 1959), pp.388—389.
78Gabriel Paquette, Imperial Portugal in the Age of Atlantic Revolutions: The Luso-Brazilian World, c. 1770—18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80;Carl E. Solberg, “Peopling th e Prairies and the Pampas: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Argentine and Canadian Agrarian Developmen t, 1870—1930”,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 24, No. 2(May 1982), p p.131—161;Adam Giesinger, From Catherine to Krushchev, p.229;Frederick C. Luebke, Germans in th e New World: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mmigration(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0), p p.94, 96.
79Warren Dea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o Paolo: 1880—1945(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9), p.35.
80Carl Solberg,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sm, Chapter 1;George F. W. Young, “Bernardo Philippi, I nitiator of German Colonization in Chil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51, No. 3(A ugust 1971), p.490;Fred C. Koch, The Volga Germans, pp.231—233.
81Fernand Braudel,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translated by Richard Mayne(New York:Penguin Book s, 1993), p.440.
82J. F. Normano and Antonello Gerbi, The Japanese in South America: An Introductory Survey with Sp ecial Reference to Peru(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 1943), pp.38—39.
83C. Harvey Gardiner, The Japanese and Peru: 1873—1973(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 ss, 1975), p.25;J. F. Normano and Antonello Gerbi, The Japanese in South America, p.70.
84C. Harvey Gardiner, The Japanese and Peru, pp.62, 64;Toraji Irie and William Himel, “History o f Japanese Migration to Peru, Part II”,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31, No. 4(Nove mber 1951), p.662.
85C. Harvey Gardiner, The Japanese and Peru, pp.61—62.
86William R. Long, “New Pride for Nikkei in Peru”,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8, 1995, p.A1.
87Pablo Macera and Shane J. Hunt, “Peru”, Latin America: A Guide to Economic History, 1830—1930, edited by Roberto Cortés Conde and Stanley J. Stei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 7), p.566.
88C. Harvey Gardiner, The Japanese and Peru, p.68;J. F. Normano and Antonello Gerbi, The Japanese in South America, pp.109—110. 89C. Harvey Gardiner, The Japanese and Peru, p.68.
90J.F. Normano and Antonello Gerbi, The Japanese in South America, pp.77, 113—114.
91Carl Solberg,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sm, p.63.
92Seymour Martin Lipset, “Values, Educ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lites in Latin America, edi ted by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Aldo Solari(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24—25.
93Jaime Vicens Vives, “The Decline of Spai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 edited by Carlo M. Cipolla(London:Methuen & Co., 1970), p.127.
94Norman R. Stewart, Japanese Colonization in Eastern Paraguay(Washington:National Academy of Sc iences, 1967), p.153.
95Harry Leonard Sawatzky, They Sought a Country: Mennonite Colonization in Mexico(Berkeley:Unive 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365.
96Lawrence E. Harrison, The Pan-American Dream, p.83.
97Josep.Stiglitz, “Equal Opportunity, Our National Myth”,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7, 2013, Sun day Review, p.4.
98Jason L. Riley, Please Stop Helping Us: How Liberals Make It Harder for Blacks to Succeed(New Y ork:Encounter Books, 2014), p.49.
99John U. Ogbu, Black American Students in an Affluent Suburb: A Study of Academic Disengagement (Mahwah, 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3), pp.23—31.
100比如见Diana Furchtgott-Roth and Christine Stolba, Women’s Figures: An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 Economic Progress of Women in America(Washington:The A. E. I. Press, 1999), Part II;Thomas Sow ell, Economic Facts and Fallacies, second edition(New York:Basic Books, 2011), Chapter 3。
101“The Economic Role of Women”, The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73(Washington:U. S. G 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p.105.
102统计数据见我的另一本书, Affirmative Action Reconsidered: Was It Necessary in Academia?(Washing ton: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75), p.16。
103Donald Harman Akenson, “Diaspora, the Irish and Irish Nationalism”, The Call of the Homeland: Diaspora Nationalisms, Past and Present, edited by Allon Gal, et al(Leiden:Brill, 2010), pp.190 —191.
104Karyn R. Lacy, Blue-Chip Black: Race, Class, and Status in the New Black Middle Clas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66—68, 77;Mary Pattillo-McCoy, Black Picket Fences: P rivilege and Peril Among the Black Middle Clas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1
105Donald R. Snodgrass,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laysia(Kuala Lumpur:Oxford Univ ersity Press, 1980), p.4.
106Amy L. Freedman,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Policy and Institutions on Chinese Overseas Accultu ration:The Case of Malaysia”,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35, No. 2(May 2001), p.416.
107Michael Ornstein, Ethno-Racial Inequality in the City of Toronto: An Analysis of the 1996 Censu s, May 2000, p.ii.
108Charles H. Young and Helen R.Y. Reid, The Japanese Canadian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 ess, 1938), pp.9—10, 49, 53, 58, 76, 120, 129, 130, 145, 172;Tomoko Makabe, “The Theory of the Split Labor Market:A Comparison of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in Brazil and Canada”, Social Forces, Vol. 59, No. 3(March 1981), p.807, note 1.
109John A. A. Ayoade, “Ethnic Management of the 1979 Nigerian Constitution”, Canadian Review of Studies in Nationalism, Spring 1987, p.127.
110Burton W. Folsom, Jr., The Myth of the Robber Barons: A New Look at the Rise of Big Business in America, sixth edition(Herndon, Virginia:Young America’s Foundation, 2010), pp.83—92.
111Rob Kl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Shifting Balance between Privacy and Social Contr ol”, Computerization and Controversy: Value Conflicts and Social Choices, second edition, edited by Rob Kling(New York:Academic Press, 1996), p.617.同时见Marvin Cetron and Owen Davies, Probabl e Tomorrows: Ho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Transform Our Lives in the Next Twenty Years(New Yor k:St. Martin’s Press, 1997), p.x。
112Richard A. Epstein, Overdose: How Excessive Government Regulation Stifles Pharmaceutical Innova 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5.
①中国西周数学家商高在西元前1000年就发现勾股定理的一个特例:勾三,股四,弦五。
②成年人中的年轻人需要若干年才能让自己的净财富变成0,因为处在这一年龄段的人通常由于大学贷款、汽 车、家具等支出背负超出他们储蓄额的债务。与此同时,年过六十的老人早已跨过此阶段,积攒了数十年的积蓄,拥有房屋不动产,或许还将钱投入了养老金计划。不考虑阶层不平等,不同年龄人群间的财富差异也会很 大。
③在第三世界建厂的跨国公司付给工人的工资通常比当地的雇主高一些。
④伯克经常弹劾英国印度总督压迫当地人。除此之外,在废奴思想还是西方文明中少数人认可的观点时,伯克就推动了废奴运动,甚至还起草了让奴隶为自由做好准备以及为他们作为自由人开始新生活提供财产的计划。米尔顿·弗里德曼提议全面改革公立学校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并提出对穷人征收负的所得税进行转移支付。伯克曾说过:“没有变革手段的国家,也就没有保存自己的手段。”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著有《现状的暴政》(The Tyranny of the Status Quo)一书。
致谢
致谢总有些陈词滥调,比如我们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对于那些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撰写不朽巨著的研究者,我始终心存敬畏和感谢。这些著作包括维克托·珀赛尔(Victor Purcell)的《华人在东南亚》(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查尔斯·穆雷 (Charle Murray)的《人类的成就》(Human Accomplishment)、斯蒂芬·特恩斯特伦 (Stephan Thernstrom)和阿比盖尔·特恩斯特伦(Abigail Thernstrom)的《黑人和白人的美国》、艾伦·丘吉尔·萨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的《地理环境之影响》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唐纳德·L. 霍洛维茨的《冲突的族群》, 还有N. J. G. 庞兹关于欧洲历史与地理的一系列博学并富有洞察力的著作。
其他一些著作或许篇幅不长,却以其极高的品质闻名于世。其中包括西奥多·达林普尔的《底层人的生活》、查尔斯·A.普莱斯(Charles A. Price)的《澳大利亚的南欧人》 (Southern Europeans in Australia),以及大卫·S. 兰德斯著《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另外,我在写作中参考或引用过的数以百计的其他论文和著作同样值得一阅,可作为参考读物。
如果我们只是站在巨人及前人的肩膀上,不过是重复他们所看到并已完美阐述的事情,那将毫无意义。不过,我们仍然是站在他们提供的有利位置上,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世界。
我们也会发现,还有许多执迷不悟的出版物,包括“徒有其表”的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书。这些读物激发我去思考以前从未关注的议题。我在文中也提到这些执迷于错误观念而不悔改的作者,不过他们或许并不会感激我在书中提到他们的名字。
言归正传,我要感谢我的研究助理刘娜(Na Liu)和伊丽莎白·科斯塔(Elizabeth Costa)。毫不夸张,她们对我的恩情难以言表。她们不仅为我找到了要求的研究资料, 而且还搜寻和评估了大量其他研究资料,积极地参与研究。除此之外,科斯塔女士承担了编辑和校对工作,而刘女士建立了精准的电脑文件,以使文稿达到可以直接印刷出版的程度。
当然,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胡佛研究所的支持和赞助。在此过程中,我还利用了斯坦福大学丰富的图书馆藏。我的妻子玛丽以及老友约瑟夫·查尼(Joseph Charney)评论了第一章初稿,根据他们的意见,我对该章做了较大修改并有了改进。
所有的结论以及任何错误,我个人愿意承担责任。
托马斯·索维尔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How An Economy Grows And Why It Crashes
- 概述
- 正文摘录
- 推荐序
- 珍藏版序言
- 序 言
- 写在前面
- 第一章 一個好點子出爐了→經濟利益的產生
- 第二章 把財富分享給別人→金融思維
- 第三章 信用貸款的多種用途→信用供給
- 第四章 經濟到底是如何發展的→經濟效益:儲蓄大於消費
- 第五章 在魚被指定為貨幣之後→效率、通貨緊縮
- 第六章 為什麼會有儲蓄→經濟崩盤的前兆、低利率的影響
- 第七章 基礎建設與貿易→建設是成長或浪費?
- 第八章 一個共和國就這樣誕生了→權力、自由、約束
- 第九章 政府的職能開始轉變了→發行魚券
- 第十章 不斷縮水的魚就像貨幣一樣→支出 > 儲蓄、通膨問題
- 第十一章 中島帝國:遠方的生命線→國外需求與貿易
- 第十二章 服務業是如何崛起的→美元地位、貿易順差
- 第十三章 「魚本位」的破滅→再次通膨
- 第十四章 小屋價格是如何漲上去的→質借、政府政策影響房價
- 第十五章 快了!快了!小屋市場要崩潰了→財富假象、政府干預阻止重新分配
- 第十六章 情形怎麼變得如此糟糕→消費降低、失業率提高、國外融資
- 第十七章 緩兵之計→量化寬鬆政策的問題
- 第十八章 佔領華夫街→錢的錯誤分配
- 第十九章 無魚不起浪→惡性通膨、重回無經濟活動的魚網捕魚
- 后 记
概述
前言
本书最重要的章节是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
第四章最后一句:
储蓄创造了资本,而资本使生产扩大成为可能,所以储蓄起来的一美元对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要大于消费掉的一美元。对于这一点,你不必费力向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家解释。
作者强调在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大于消费,用于投资的一美元比用于消费的一美元作用要大。没有生产也就无法消费。从国外进口也得付账。
如果社会中个体深陷于消费主义而不重视储蓄和投资,最终会使整个社会崩溃。
书籍简介
作者: 【美】] 彼得・希夫 / 【美】安德鲁・希夫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鱼、美元和经济的故事
原作名: How An Economy Grows And Why It Crashes
译者:胡晓姣 / 吕靖纬 / 陈志超
出版年: 2016-9
定价: 59.00 元
装帧:精装
ISBN: 9787508649221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原理简化与通俗化的经济理财书籍。通过一个虚构的小岛,作者以讲故事的方式,将复杂的经济学原理,简化为易于理解的语言和实例,使得经济学变得不再复杂。书中通过艾伯、贝克和查理的故事,展示了创新思维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通过创新思维,提出制造更大更好的资本设备,如建造巨型捕鱼器,从而提高了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使得他们的储蓄迅速增加,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发展。书中还通过美索尼亚国与中岛帝国的贸易合作,展示了国际贸易和经济模式的一些基本概念。中岛帝国通过贸易合作,学习美索尼亚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而美索尼亚国则可以扩大市场,增加就业机会。此外,书中还通过政府支出与纳税人权利的关系,揭示了政府支出与纳税人权利之间的平衡。政府需要资金来运作,但纳税人有权知道他们的钱是如何被使用的,以及他们的权利如何被保护。这种平衡对于任何民主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简介
彼得・希夫 Peter D. Schiff
著有暢銷書《美元大崩潰》(Crash Proof 2.0: How to Profit from the Economic Collapse)和《未來十年,這樣做才能致富》(The Little Book of Bull Moves in Bear Markets),兩本書皆由 John Wiley Sons 出版。他是經驗老到的華爾街預言家,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他曾準確預測西元 2008 年的金融風暴。希夫曾任職希爾盛雷曼公司(Shearson Lehman),後來於 1996 年加入歐洲太平洋資本公司(Euro Pacific Capital 一家專門操作國外市場和證券的券商),並於 2000 年升任總裁。他的見解常被各大媒體引用,包括《華爾街日報》、《巴倫周刊》、《金融時報》和《紐約時報》等,也曾上過「股市擴音器」(Squawk Box)、「收盤鈴聲」(Closing Bell)、Fox 新聞等電視節目。2009 年,他宣布角逐家鄉康乃狄克州參議員候選人。
安德魯・希夫 Andrew J. Schiff
身兼歐洲太平洋資本公司公關主任、資深發言人。他精通媒體關係和金融公關,常常在各大研討會和電視節目中發表言論,宣揚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與有限政府的觀念。閒暇之餘,喜歡閱讀歷史書籍、觀賞各類建築,並彈奏曼陀林。
正文摘录
推荐序
小岛经济开启智慧之门 这是一本别具一格、引人入胜的经济学著作。
从小岛开始,一个个原本深奥的经济学原理便在一个个故事中生动地体现出来。随着故事层层思考下去,便会发现,尽管一些经济学的道理看起来越来越深入,却始终贴近我们的实际,并始终充满乐趣。
既能言简意赅地讲明道理,又保持着足够的吸引力,使得读者好像在一种魔力的吸引下享受阅读,是极难做到的,而彼得・D・希夫与安德鲁・J・希夫做到了,《小岛经济学》是一本难得一见的好书。
但如果将这本书仅仅看作经济学入门读物,我觉得有失公允,因为这本书对当下的很多经济现象做了深刻的剖析,并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喜欢这种鲜明的风格。我甚至认为,如果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或执行者能够明白其中的一些道理,一定不会在诸如以庞大政府投资主导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诚如作者所言,“凯恩斯主义允许政府摆出一副有能力提高生活水平的模样,只要印钞机运转,什么公开承诺都可以做。因为存有亲政府的倾向,凯恩斯主义者们比奥地利经济学派更有可能接受政府的最高经济任职”。
凯恩斯的主张为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找到了合理的理由和依据,却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因为它使经济自身的运行规律遭到破坏,使得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被扼杀。
当下的中国不正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吗?不加息,流动性泛滥,通货膨胀必然日益严重;加息,由于不能对政府投资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反而加速了民营企业的大面积死亡,而这些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恰恰是市场所需的。这意味着,当这些生产企业次第倒闭,供应减少,反而会加速中国的通货膨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两难的局面?根源就在于,政府成为经济的主导者,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角。这种困局只有当政府的职能从主导经济向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过渡以后,才能真正得以改变。
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是催生天量货币不断被滥发的根源。政府通过通货膨胀稀释民众的财富,通过悄悄盗用民众的财富满足所谓的经济干预计划,而这些计划无不是被种种动听的承诺包装着,尽管这些动听的承诺很少真正兑现。
政府为了使通货膨胀的理由变得生动可人,不断妖魔化通货紧缩:“现代经济学错误地认为: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因而一旦发生通货紧缩,人们就不愿意消费(这样价格就会继续下降),而人们如果消费,价格下降的影响就会减弱。真是荒谬。”
是的,这是荒谬之极的理论,它甚至在常识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还有什么比让物价降低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对消费者更具有吸引力呢?
《小岛经济学》中讲述的一些基本道理,帮助我们回归常识。
无论是大规模经济还是小规模经济,所遵循的经济学原理是一样的。比如,投资建设,“只有在收益大于支出时,这种投资才有效益。反之,这些项目就是在浪费资源并会阻碍经济增长”。但很多人似乎只看到了投资建设带来的毫无意义的虚幻的 GDP(国内生产总值)数字,却没有看到这种高投资低回报甚至无回报的结果所带来的巨大的财富损耗。
从这个角度来看,《小岛经济学》讲述的故事其实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当我们倾听了这些故事,明白了这些故事背后的经济逻辑脉络,对于很多经济现象便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或许正是《小岛经济学》的价值所在吧。
我曾经拜读过彼得・D・希夫的《美元大崩溃》(Crash Proof),对其大胆、明确、一针见血的风格非常欣赏。彼得・D・希夫与安德鲁・J・希夫合作的这本《小岛经济学》具有同样鲜明的风格。愿这部著作让更多的读者从中受益。
时寒冰
珍藏版序言
自《小岛经济学》一书问世以来,已有 4 年之久。4 年来,我们始终与读者保持交流,与他们探讨如何运用书中理论来稳定美国及其他国家持续动荡的经济,这也是本书写作的初衷。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仍旧觉得自己尚有未尽之言,未尽之责。
本书第 1 版写作手法幽默,内容浅显易懂,有关鱼的双关比喻也算生动,但在品质方面仍有所欠缺。另外,第 1 版也有造作之嫌,貌似我们想利用低廉的价格吸引那些对经济学原理不够了解的读者,以此获得庞大的读者市场。但现在,我们坚信许多忠实的读者正满心期待这本书有一个更加细致完善的新版本,更有许多读者可能会将本书作为礼物赠人,或者作为展示摆放在咖啡桌上,因此我们由衷地希望能将本书打造成馈赠佳品、阅读精品。
由此,我们决定推出本书的 “珍藏版”。这个版本比第 1 版内容更丰富,也更翔实。我们对新版的扉页做了美化处理,在书中加入了一些新插图,纸张的质量也有了提高,比第 1 版更平整更光滑。在写作模式上,新版基本延续了第 1 版的故事书的形式,我们始终觉得这样的形式与本书的精神最为契合。上述只是本书包装上的改进,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内容上做了许多增补。
本书第 1 版问世之时,正值美国经济近乎完全崩溃一年之后。自那时起,形势已经有了明显好转。时至今日,我们不再整天报道低迷的 GDP 增长,房地产市场呈现回暖态势(一些市场的价格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攀升),股票市场不断创造历史新高,通货膨胀貌似又回到可控范围内,失业率也在稳步下降。但与此同时,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些所谓的 “经济复苏”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
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美国中等收入家庭在 2013 年 8 月的收入比 2008 年经济大萧条开始前还要低。当时越来越多的人面临失业,或者只能做兼职工作,然而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一份全职工作。但那些新出现的全职工作,更多的是在低薪的零售业或服务业,而非待遇优厚的中产阶层岗位,这些岗位正日趋减少。今天的大学毕业生正面临着史上最为惨淡的就业前景,即便毕业时负债累累,他们也没有理由得到好的岗位。
在当下的美国社会,人们旅游和度假的花销越来越少,更多的工资都拿来买生活必需品(食物与能源)了。如今美国马路上飞驰的汽车,全都是老得不能再老的旧款式,曾经代表着美国经济实力的龙头城市底特律,如今也惨遭破产厄运。这一切,绝非偶然。
我们听到的总是经济正在复苏的消息,实际上却面临着令人失望的前景,所闻与现实之间根本就是天壤之别。这是因为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为避免承担更大的损失,联邦政府开始花费我们实际并没有的数万亿美元,美联储也开始实施一项名为 “量化宽松” 的新政策。这些政策已经成为实体经济的替代品。
10 年前,除了在大学经济系之外,几乎没有人听过 “量化宽松” 这个名词;时至今日,这一政策已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手。众多投资者与财经新闻工作者近乎痴迷地紧跟联邦政府这一政策,就像 14 岁的校园女生追随着她们最爱的男孩乐队(Boy Band)一样。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仿佛已变身为加拿大流行音乐小天王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备受追捧。
然而,量化宽松不过是 “印钞票” 的一种花哨的委婉说法而已。自 2010 年起,美联储凭空印发了数万亿美元用来购买资产,包括政府支持的债券和抵押贷款债券。这些做法抬高了相关市场的价格,降低了长期利率。美联储正利用印钞机的力量创造一个经济复苏的假象。但这种创造出来的经济和作为其支撑的那些印刷的钞票一样,都是假象。在这种如履薄冰的健康假象之下,经济发展甚至比美联储采取补救措施之前还要惨不忍睹。
举例来说,在我们准备推出《小岛经济学》一书的新版本之际,美联储也在购买每月 450 亿美元的国债,占据了政府发行的所有债券的大部分。这一举措使得长期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发展。美联储鼓励公司和个人借贷,不支持他们储蓄。极低的利率也是近几年推动股票市场迅猛发展的主要原因。如果美联储停止购买债券,利率便会立即飙升,股票会暴跌,看上去健康的经济也会消失不见。
量化宽松政策对房地产行业的复兴也有直接的影响。美联储每月购买 400 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券,实际上相当于已经认购了房地产市场。但美联储所购买的抵押贷款,是个人买家出于合理原因根本不愿意碰触的。房价仍然与收入高度相关,大多数买房者没有足够的储蓄来支付巨额的首付款。但政府的担保人只需要支付最低首付款,再加上有美联储提供的超低利率,支付相对轻松很多。假如没有这些支持,房地产市场毫无疑问会像 2008 年金融危机时一样崩溃失衡。
因此,量化宽松政策已经成为美国的经济命脉这一说法并不为过。但问题在于,这一政策诱惑性极大,最终会毒发不治。我们实现了基于量化宽松政策的人为经济复苏,这种复苏也只能与该政策同生共灭,并不能为真正的经济复苏奠定基础。
目前,主流经济学家都在讨论,在不损害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美联储会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摒弃量化宽松政策(即所谓的 “退出策略”)。尽管多数人承认实施 “退出策略” 会遇到重重阻力,但他们仍然相信,手段高明的执行者会以极其灵敏精确的方式完成这项任务。这就好比一个古老的戏法:将桌布从一张摆满东西的桌子上猛地抽走,桌上的瓷器却纹丝不动。但这还不是美联储要表演的戏法。实际上,美联储要抽走的不是桌布,而是桌子本身。他们希望既能撤走桌子,又不让那张桌布和那些餐具掉落地上。
这就是我们认为当前经济已经陷入困境的理由。我们痴迷于量化宽松政策,却并不了解它,而经济学家期待的量化宽松 “退出策略” 则永远也不会出炉。这是一条不归路,只会带来更为严重的经济问题。
鉴于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小岛经济学》的珍藏版增加了两个新章节 —— 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 —— 旨在揭秘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最新进展)。另外,我们还对全书做了几处编辑,同时还增加了部分奖励内容。希望新增的内容会使本书与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世界联系更加紧密。
希望你们能喜欢本书,并与那些需要回归理性的朋友们分享。
彼得・D・希夫与安德鲁・J・希夫
2013 年 9 月
序 言
……
2007 年,当世界聚焦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经济灾难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并没有意识到棘手的问题已显露端倪。此后三年里经济一片混乱,经济学家们拿出的补救方案令大多数人瞠目:为了解决债务危机,我们必须负债更多;为了经济繁荣,我们必须花钱消费。过去他们缺乏远见,而今他们的解决方案又如此违背常识,究其原因,是因为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明白他们的学科如何发挥作用。
凯恩斯创造了许多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其中就包括上述那些荒谬的建议。凯恩斯是 20 世纪早期非常有头脑的英国学者,但他却提出了一些非常愚蠢的理论来分析经济增长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凯恩斯只不过是玩了一个聪明的把戏而已,他把一件简单的事情搞得极其复杂。
在凯恩斯的时代,物理学家们首次提出了量子力学的概念。量子力学是研究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物理学分支学科,它认为宇宙是受两套截然不同的物理规则制约的:一套规则对极小的粒子产生作用,如质子和电子;另一套则对其他所有事物产生作用。也许是觉得经济学理论太枯燥,需要加点儿新鲜手法,于是凯恩斯提出了一个类似量子力学的经济学研究视角,创造了两套经济规律,一套作用于微观层面(与个人及家庭生活相关),另一套作用于宏观层面(与国家和政府相关)。
凯恩斯的理论提出时,适逢全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繁荣期即将结束。从经济角度来讲,19 世纪与 20 世纪早期西方世界的产能增长水平与生活水平都是空前的,而此次经济繁荣的中心就是实行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美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维护个体权利、限制政府权力。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权力分散,因此这一体制在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对原有的僵化权力结构构成了威胁。此外,资本主义的扩张导致明显的贫富两极分化,促使一些社会学家和进步人士开始寻求他们眼中的公平正义,以取代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体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凯恩斯在看似不公平的市场经济中引入现代科学的概念。这种做法无意中迎合了国家权力中心和社会理想主义者的心态,使他们相信经济活动的确需要凯恩斯式的规划思路。
凯恩斯的核心观点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可以通过扩大货币供给和财政赤字缓和自由市场的波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凯恩斯的追随者(即凯恩斯主义者)们崭露头角,与支持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等经济学家观点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产生了冲突。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衰退是经济繁荣期所做出的错误决定的必要补偿,经济迅猛发展过后必然会有一个相应的衰退期。他们认为,政府利用低利率 “刺激” 经济的做法向各个企业发出了错误的信号,这才是经济繁荣的首要原因。
因此,凯恩斯主义者力图缓解经济萧条,而奥地利学派则寻求避免虚假繁荣的途径。在两者随后的经济理论论战中,凯恩斯主义者有一个关键优势。
凯恩斯主义使人们以为可以拿出解决经济危机的无痛方案,因此立刻受到政治家们的追捧。凯恩斯倡导的各项政策承诺提高就业率,在税收不增加、政府服务不减少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发展,这些政策与那些无须节食、无须运动的神奇减肥计划一样具有魔力。尽管这些愿望不合常理,但却令人颇感慰藉,因此成了竞选活动中惯用的手法。
凯恩斯主义允许政府摆出一副有能力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模样,只要印钞机开动起来,什么都可以做到。因为具有亲政府的倾向,凯恩斯主义者们比奥地利学派学者更有可能接受政府的任命。那些培养出数位金融大臣和财政部部长的大学的声望明显高于没有这些成就的大学,各大学经济系也不可避免地青睐那些支持凯恩斯主义的教授,而奥地利学派则不断受到排挤。
同样,那些大型金融机构和众多经济学家效力的大雇主也都对凯恩斯的主张青睐有加。大银行和投资公司利用凯恩斯主义者创造的低息贷款和宽松货币政策等经济条件,赚得盆满钵满。另外,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政府政策应当鼓励投资,这一理念也帮助金融公司把手伸进了很多头脑发热的投资者的钱袋。因此,这些金融公司更倾向于雇用那些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
与呆板守旧的竞争对手相比,凯恩斯主义者有着明显的优势。于是,一个自我实现、相互吹捧的社会很快催生了一大批热衷于凯恩斯主义原则的顶级经济学家。
这些经济学家将凯恩斯政策奉为真理,认为它可以结束大萧条的局面。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如果没有政府出台的刺激政策(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必需的军费),我们永远也无法从经济衰退的绝境中恢复元气。事实上,此次大萧条是现代历史上历时最长、程度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凯恩斯政策在这次经济衰退中首次得到了全面而充分的运用。至于这些政府干预措施究竟是不是经济萧条得到遏制的原因,这个问题至今为止仍然充满争议,但是所有正统的 “经济学家” 都认为这种争论没有什么价值。
如果我们允许凯恩斯主义者们牢牢控制着多个经济部门、金融部门以及投资银行,那跟我们委托占星师而不是天文学家测量天体的运行速度是一样的。(是的,卫星曾经撞击过小行星,但那只是一次不期然的偶遇,是一次美丽的意外!)
这种情形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方在于,无论经济学家们多少次彻底搞砸了自己的任务,无论有多少支火箭还没有离开发射台就爆炸了,这些责任重大的人物没有一个质疑过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
普通人慢慢明白了,其实这些经济学家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大多数人只是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因为经济领域的确太大了,并且充满风险,毫无逻辑可循,即便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也不可能拥有预知一切的能力。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凯恩斯主义者们所推崇的经济二元性根本就不存在,会怎样?如果经济学比他们所说的简单得多,会怎样?如果对母鹅有益的东西对公鹅也一样,会怎样?如果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国家不可能靠花钱实现繁荣,又会怎样?
很多人熟知我曾对 2008 年的经济衰退做过精准的预言,他们认为我的智慧决定了我的远见。我可以向你保证,大多数经济学家连自己身边的资产泡沫都看不到,而我并不比他们聪明。我具备的是对经济学基本原则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我的确具有这个优势。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就为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工具包,里面的工具可以帮助我认清经济的真实面目。这些工具以故事、寓言以及思想实验的形式出现,本书就是以其中一个故事为基础展开的。
我的父亲欧文・希夫(Irwin Schiff)拥有一定的知名度,与反对联邦所得税的全美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坚持认为所得税的强制实施违犯了美国宪法中与税收相关的三项条款、宪法第 16 修正案以及税收法律的有关规定,并在 35 年多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反对美国国税局的这一做法。他曾经就这个主题写过很多书,也曾在法庭上公开挑战联邦政府。因为这些举动,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 86 岁高龄时,他还被关押在联邦监狱中。
但是在将自己的关注点转向税收之前,欧文・希夫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了。
欧文・希夫于 1928 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一个下层中产阶级家庭,是家中的第八个孩子。他的父亲是一名工会会员,整个大家庭都是 “罗斯福新政” 的狂热支持者。1946 年,欧文进入康涅狄格州州立大学学习经济学。以他的家庭背景和性格,没有人相信他会摒弃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经济学观念,转而坚决支持过时的奥地利学派的观点 —— 但是他却实实在在这样做了。
欧文总是有独到的想法,加上对自己充满信心,他总感觉自己所学的东西与现实生活有些脱节。他深入研究了所有经济理论,广泛涉猎了亨利・赫兹利特(Henry Hazlitt)与亨利・格雷迪・韦弗(Henry Grady Weaver)等自由思想家的著作。尽管欧文的转变是循序渐进的(经历了 1950~1960 年整整 10 年的时间),但他最终成为健全货币、有限政府、低税收和个人责任的狂热信仰者。1964 年,欧文满腔热情地支持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竞选美国总统。
在 1944 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说服了全球很多国家支持美元取代黄金的做法。由于美国保证 35 美元兑换 1 盎司黄金,这个计划得到了广泛赞同,美国也因此拥有了世界上 80% 的黄金。
然而,美联储中的凯恩斯主义者造成的长达 40 年的通货膨胀导致与美元直接挂钩的黄金价格严重下跌。这种错位的现象造成了众所周知的 “黄金外流”。1965 年,由法国牵头,许多国家纷纷以美国联邦储备券(即美元)兑换黄金,以 1932 年的金价从美国手里买走了大量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备迅速减少。
1968 年,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几位经济顾问声称,那次黄金外流并非由低价出售的诱惑力所致,而是因为外国政府担心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足,无法支持本国所持有的流通货币,也无法与外币进行兑换。为解决这个令人焦虑的问题,约翰逊总统的众多金融专家纷纷献计,建议将法定用于支持本国美元的 25% 的黄金储备转为外国美元持有者的备用储备。他们认为,这项额外的保护措施将会安抚外国政府,阻止黄金的继续外流。当时的欧文只是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一个年轻的生意人,他对政府这种做法十分不解,觉得他们的观点非常荒唐。
欧文给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约翰・托尔(John Tower)写了一封信,托尔当时是黄金问题评估委员会的成员。欧文在信中说,美国政府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强行摧毁现行的价格结构,将金价恢复到 1932 年的水平;要么调高金价,与 1968 年持平。换句话说,要调整凯恩斯主义导致的长达 40 年的通货膨胀,美国政府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紧缩通货,要么让美元贬值。
尽管欧文认为通货紧缩或许是重振美国经济最有效的做法,因为通货紧缩可以使美元恢复购买力,但他觉得经济学家们错误地将价格下滑当作灾难,而政府天生具有通货膨胀的偏好(本书将对此进行论述)。出于这些考虑,他认为当权者至少要承认此前的经济下滑,并且降低美元对黄金的价值。在这样一个方案中,欧文觉得黄金的价格必须达到每盎司 105 美元。
欧文还担心另外一种可能性更大也更危险的选择:政府不作为(其实这也正是政府的选择)。当时的选择是,究竟是面对现实解决问题,还是将问题留给下一代人。当权者选择了将问题留给下一代人,而我们就是那下一代人。
托尔对欧文论证问题的基本逻辑印象深刻,他邀请欧文为黄金问题评估委员会全体委员做报告。在这次听证会上,来自美联储、美国财政部以及国会的高级货币专家们都证实,与黄金脱钩将会增强美元的购买力,降低金价,引领美国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阶段。
在其证词中,欧文却坚持认为,美元与黄金脱钩会导致金价飞涨。更重要的是,他还警告说,一种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货币会导致大规模通货膨胀以及无法持续的政府负债。但在当时,这种少数派的意见完全被忽视了,美国政府取消了金本位制。
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相反,额外的储备未能阻止黄金的外流。最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于 1971 年彻底切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从此以后,全球经济体系完全建立在没有任何价值的美元之上。接下来的 10 年里,美国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黄金价格直逼每盎司 800 美元的天价。
1972 年,欧文在其著作中展开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首次全力攻击。在书中,他指出凯恩斯经济学将美国引向了一条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之路。这部名为 “最大的骗局:政府是怎样欺骗你的”(The Biggest Con: How the Government Is Fleecing You)的著作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销量也相当可观。书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三个人在一座小岛上徒手捕鱼的事。
这个故事是欧文在一次全家自驾游时为了消磨时间讲的。当时堵车,欧文就想给两个年少的儿子讲点儿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任何男孩都会对此感兴趣)。为了让两个儿子开心,他总会讲些有意思的故事。这次讲的就是 “鱼的故事”。
这个故事构成了《最大的骗局》一书中其中一章的主要内容。大约 8 年之后,由于众多读者反映非常喜欢他写的故事,欧文决定将这本书改版为有插图的书,并命名为 “经济增长模式与停滞的原因”(How an Economy Grows and Why It Doesn’t)。这本书于 1979 年首次发行,受到了奥地利学派追随者的狂热追捧。
30 年后,我看着美国经济垂死挣扎,看着美国政府不断重复和加深过去的错误,此时,我的弟弟和我觉得要为新一代修改和更新 “鱼的故事”,现在正是最佳时机。
当然,现在人们最需要的是了解经济的真实情况,而这个故事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佳工具,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是什么在推动经济的运行。
我们这个版本的故事在很多方面比我们的父亲欧文 30 年前的那个版本更富有雄心。我们的视野更宽,为使故事与历史脉络衔接自然,我们付出了更大的努力。事实上,我们的故事应该说是在父亲那个故事基础上的即兴发挥。
听到经济学家们喋喋不休地谈论与现实生活看似毫无关联的概念时,有些人会不知所云。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吸引这些读者。我们打算证明凯恩斯主张的经济模式(政府相信没有价值的货币可以作为有效的经济润滑剂并不加证实地采纳了这个模式)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可惜,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忘记了他们正戴着玫瑰色眼镜。当你摘下他们的眼镜时,就会清晰地看到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很多严重的问题,而我们非但没有使形势好转,反而使它变得更加糟糕。幸运的是,如果我们重新理清思路,我们至少还有机会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本书的主题非常严肃,但在这个压力巨大的时代,我们选择了一种幽默的方法阐释这个主题 —— 这也是我们的父亲欧文的愿望。
写在前面
在这个关于美国经济史的寓言故事中,读者会遇到很多似曾相识的人物与事件。但是,要将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浓缩为一部漫画式作品,只能进行粗线条的描述。
除了特定历史人物的辉煌成就之外,故事中的人物代表着更宽泛的概念。例如,本・伯南柯的原型很明显是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但故事中伯南柯的所作所为却不是单纯指伯南克本人的做法,他其实是所有主张高通货膨胀率的经济学家的代表。
在现实生活中,美国联邦储备券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前 20 年就已经出现了。但考虑到他有花钱的嗜好,于是我们决定将这一创新归功于他;当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前主席克里斯・多德(Chris Dodd)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房利美(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因为他多年来对该公司的扶持,在我们的故事里,我们赋予他公司创始人的身份。还有,尽管本书提到的那些外国岛屿基本上都与真实的国家相关,但这些岛屿也是所有国家的化身。我们对某些历史事件及人物经历进行了艺术处理,请您多多包涵。
第一章 一個好點子出爐了→經濟利益的產生
查理嚇得眼珠直轉,他想自己的朋友肯定是瘋了。「你瘋了,這樣做,我告訴你…… 瘋了。要是你這捕魚器不好用,可別哭著來跟我要魚吃,一片也別想。我頭腦清醒,但這並不表示我會為你的瘋狂做法買單。」
故事引申
在这个简单的任务中,艾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基本的经济原则,这个原则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消费不足,敢于冒险!
消费不足:为了织网,艾伯那天就不能去捕鱼。他必须放弃当天的所得,放弃那条本来可以捕到、吃到的鱼。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不需要鱼,事实上,他爱吃鱼,而且如果那天没有捕到鱼,他就会饿肚子。他对鱼的需求与他的两个朋友没有什么不同。他选择暂时延迟消费(吃鱼),是为了将来消费更多的产品(捕到更多的鱼)。
冒险:除了消费不足,艾伯还需要冒险,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捕鱼器到底好不好用。自己花费了一天的时间饿着肚子辛苦劳动,却不知道这东西究竟能不能补偿所失。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只剩一把绳子和一个饿瘪的胃。如果这个想法失败了,艾伯不能指望贝克和查理给自己任何补偿,因为他俩早就警告过他这样做很傻。
在经济学术语中,资本指的是一种设备,这种设备的建设和使用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其意义在于利用设备建设和制造其他需要的东西。艾伯想要的不是那张网,而是鱼。这张网或许可以给他带来更多的鱼。因此,这张网就是一种资本,是有价值的。
故事引申
艾伯的生产力提高了一倍,现在他生产的东西多于自己需要消费的东西。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许多益处。
在艾伯孤注一掷去编织渔网之前,小岛上还没有什么储蓄之所。他决定冒险挨饿制造的这张网成了小岛上的第一件资本设备。这件设备接着会带来储蓄(为了让这个故事能够继续进行,我们假设这些鱼不会腐烂变质),而这种剩余产品就是健康经济的命脉。
现实链接
对所有物种而言(人类除外),经济学其实可以简单理解为日常生存活动。食物短缺、天气恶劣、食肉动物的威胁、疾病的困扰、发明相对较少、忍饥挨饿地活着(有一点儿剩余时间进行再生产),这是所有动物的生存常态。所幸我们人类拥有两样东西 —— 我们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否则我们的命运跟那些动物不会有什么分别(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我们跟它们是一样的)。靠着大脑和灵巧的双手,我们制造了工具和机器,改造环境的能力大大提高。
经济学家托马斯・伍兹(Thomas Woods)喜欢用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测试学生:如果所有的机器和工具都不复存在,我们的经济会是什么样子?汽车、拖拉机、炼钢炉、铲子、独轮(手推)车、锯、斧头、长矛等,如果这些东西真的全都消失了,我们所有的消费品都要靠自己的双手猎取、采摘、种植和制作,那会是什么样子?
毫无疑问,那样的生活肯定很艰苦。如果我们必须赤手空拳地制服猎物、将其作为食物的话,想象一下那该有多艰难吧。以我们的能力根本不可能逮住大家伙,兔子或许还有可能 —— 但你总得先抓住它们啊。如果我们必须用手种菜、摘菜,如果我们连装粮食的麻袋都没有的话,又会怎样?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工厂,我们必须自己缝衣服、做家具,而且连最起码的剪刀和钉子都没有,那又会怎样?
尽管我们有智慧,但我们过得可能并不比黑猩猩和猿猴好多少,至少从经济方面来看是这样。
工具改变了一切,使经济的出现成为可能。长矛帮助我们捕获猎物,铲子帮助我们种植庄稼,渔网帮助我们捕鱼。这些工具提高了我们的劳动效率。我们生产的东西越多,可以消费的东西就越多,我们的生活也就变得越美好。
努力使有限的资源(每种资源都是有限的)产生最大的效益以尽可能满足人类的需求,这就是经济这一概念最简单的定义。工具、资本以及创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牢记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经济增长的原因:找到了生产人类所需物品的更好方式。不管一个经济体最后变得多么强大,这个原因是不会改变的。
第二章 把財富分享給別人→金融思維
貝克走近艾伯,說道:「我們做個約定吧:你借給我們一條魚,我們會還你兩條,這可是百分之百的利潤啊。除了這座小島,你到哪兒能找到這樣的高報酬?」
艾伯,那个企业家,看起来前途一片光明。但是,小岛上另外两个人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是不是创造了一个贫富分化的等级体系?贝克和查理会因为艾伯的成功而不安吗?不大可能。虽然艾伯从来没有刻意使他人受益,但他的资本无疑帮助了岛上的所有人。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亲眼见证了艾伯轻松捕鱼的全过程,贝克和查理央求他分享新发明的捕鱼器。
“嘿,艾伯!” 查理说,“既然那玩意儿你隔天才用一次,那你不用的那天,让我用用行吧?”
贝克说:“喂,老兄,有福同享啊。”
但是艾伯还对昨天的事情耿耿于怀。他还记得自己的牺牲…… 他还记得他们俩的嘲讽,而且他还想到了风险。“如果他们把我的渔网弄破了怎么办?如果他们不还我怎么办?那我就要从头再来了。再见,穿树叶的哥们儿!”
想到这些,艾伯拒绝了两人的要求。“对不起,哥们儿。我自己做了渔网,你们俩肯定也能自己做,至少你们现在知道那东西是有用的,对吧!”
尽管查理已经看到用渔网捕鱼的效率,但他很担心自己能不能编织出这样一张网。
他对艾伯说:“我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编织出来?我以前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东西,而且我也挨不了饿。我怕自己织好网前就饿死了!”
贝克提出了另外一个建议:“好吧,你这个吝啬鬼,看来你是不会帮我们什么忙了。我们知道了。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编织渔网时,你把富余的鱼借给我们吃,那样我们织网时就不用挨饿了。等我们捕到多余的鱼,再把鱼如数还给你。”
尽管艾伯觉得这个办法比白白把网借给他们要好,但他还是不放心。“如果我把鱼借给你们,怎么保证你们不会躺在沙滩上一整天都不干活呢?即使你们织出自己的网来,也许还不好用呢。如果那样,你们就永远无法还我鱼了,而我失去了自己的储蓄,一无所有了!你们总得想一个更好的办法。”
查理和贝克这才明白,他们让艾伯冒险把鱼借给自己,却没有考虑到他的个人利益。但是捕到更多鱼的诱惑太大了,所以两人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办法,让艾伯忍不住冒险一试。
他们认为必须在数字上做文章,于是金融思维诞生了!
贝克走近艾伯,说道:“我们做个约定吧:你借给我们一条鱼,我们会还你两条。这可是百分之百的利润啊。除了这座小岛,你到哪儿能找到这样的高回报?”
艾伯动心了。“我对这个约定很感兴趣!” 他的语气中没有任何迟疑。
艾伯想到了那些财富:“如果我借给他们两条鱼,就能收回 4 条。也就是说,我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得到两条鱼。那我岂不成了一个鱼老板啦!”
也许有些人觉得艾伯有些过分了。如果这个故事是一部好莱坞电影,他这时肯定会得意地捻着自己打了蜡的胡子。他这是在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靠别人的辛苦劳动获利!
但是这样评论艾伯是不恰当的,因为即便艾伯的动机只是想赚些鱼,他的贪婪也可能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益处。
有一点很重要,我们要知道艾伯并不是一定要把鱼借给别人,他还有其他方案,包括以下 4 个选择:
-
他可以把鱼留下,留着自己以后吃 —— 这是最保险的选择。这样,他不会有任何损失,当然,他的储蓄也不会有什么增长。
-
他可以放纵一下,不再干活,将自己的储蓄(存下的鱼)消费掉。
-
他可以建立自己的渔网出租公司。如果艾伯每天吃掉一条富余的鱼,两天就可以再编织出两张网。
然后,他可以把多余的网租给贝克和查理,向他们收取每人每天半条鱼的租金。这样,艾伯每天不必亲自捕鱼就可以得到生存所需的那条鱼了。哈哈,提前退休!
在这个方案中,贝克和查理每天也许能用租来的渔网捕到两条鱼。在向艾伯支付半条鱼的租金之后,他们每人每天还剩下一条半鱼,比他们没有渔网时捕到的鱼多 50%,算是双赢的买卖了。
尽管这个方案很吸引人,艾伯还是注意到了其中的逻辑缺陷。贝克和查理租借渔网的时间可能只有两天,然后用富余的鱼果腹,花一天时间织出自己的网。如此一来,他能得到的鱼就只有两条 —— 那可真够冒险的!
- 他可以把两条鱼借给贝克和查理,收取 100% 的利息。在这个方案中,如果两个人按照约定利率足额偿还,艾伯就可以得到 4 条鱼。但是,这个方案也存在风险,他们可能会翻脸不认账。
抉择…… 抉择…… 艰难的抉择!
总的来说,艾伯(以及这个社会)处理储蓄(鱼)的方式只有 5 种:
-
他可以把储蓄存起来。
-
他可以把储蓄消费掉。
-
他可以把储蓄借出去。
-
他可以用储蓄投资。
-
他可以将上述 4 个方式有机结合起来。
毫无疑问,艾伯的最终决定取决于个人对风险和回报的偏好。但不管最终方案是什么,他的抉择都会惠及这座小岛的经济,而且也不会给自己的两个邻居增加负担。
最后,艾伯选择把鱼借出去。
故事引申
艾伯愿意并有能力把多余的鱼借给别人,因此,贝克和查理也拥有了自己的渔网。现在大家都有渔网可用了,小岛上的整体捕鱼能力便从每天三条鱼提高到每天 6 条鱼,经济增长翻番,前景更加光明。
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三个人对自己颇具局限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三个人对自己颇具局限性的生活方式感到不满。饥饿(其经济术语为 “需求”)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追求更多是人类的本性。不管已经拥有什么,我们总是想要更多。也许不是想要更多的东西,而是更多的时间、更多的乐趣、更多的选择,所有这些需求都需要资本。艾伯、贝克和查理这些年来对鱼的问题可能都没少抱怨,但他们最后都成功地提高了生产力,满足了自己的需求。
有了多余的鱼,小岛上的几位居民每天终于可以比原来多吃一些鱼了(原来是每天一条鱼),但是经济并没有增长,因为他们的消费增长了。而他们的消费之所以增长,是因为经济增长了。这个道理很简单,但令人不解的是现代经济学家竟然会在这个简单的问题上纠缠不休。
【评论:「但是经济并没有增长,因为他们的消费增长了。而他们的消费之所以增长,是因为经济增长了。」最后五个字应该是 “生产增长了”。】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给老百姓更多的钱花就可以增加需求,但是这种做法并不能改变真正的需求,只会使人们花更多的钱购买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只有增加供给才能切实满足人们更多的需求。
当然,有人也许并没有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共同利益。看到艾伯猛增的财富,如果贝克和查理心生嫉妒,强烈要求分得他的部分储蓄该怎么办?
设想一下这个场景:
贝克烦躁地说:“看看那家伙穿着棕榈叶做成的小礼服那副得意的样子。我们每天一身臭汗风里来浪里去地跟那些滑头的鱼斗争,他却没有一点儿善心!他就不能分给我一两条鱼,哪怕让我休息一天也好啊!他的鱼多得堆成山,少一条也没什么啊!”
查理附和道:“分给我点儿吧,贵人!”
或者再想一下下面这个场景:
假设艾伯对自己的相对财富有些负罪感,听了两个人的说法后思想动摇了,于是无偿地把鱼分给了他们,那么贝克和查理会怎样处理这些鱼呢?
没有了还款的压力,两个人最有可能做的是利用这份礼物享受闲暇时光。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事实上,这也是大多数人类行为的目标),但是贝克和查理的假日时光并不能提高这座小岛的生产能力。因此,尽管慈善之举听起来颇有雅量,也会提升艾伯的人气,但这一举动却无法像商业贷款一样推动经济发展。
最根本的是,所有能够增加捕鱼(生产)量的事物都会惠及小岛,鱼越多,大家就越有可能吃到更多东西,也就越有可能做捕鱼以外的事情,或者他们可以什么都不做。
故事引申
也许有人会想,如果艾伯果真是一个贪心的人,拿着自己的新财富生财,从而变得越来越富有,那该怎么办?
这样真的很危险吗?如果艾伯增加储蓄(而不需要亲自劳动)的唯一途径就是将这些储蓄借给自己的邻居的话,那他又何必大量囤积呢?
但若非如此,他的财产就不会增加,甚至还会越来越少,因为他自己还要消费呢!私人资本主义可以促使那些将个人利益作为唯一动机的人帮助他人提高生活水平,这是最有意义的。
现实链接
财富从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原始社会,财富是极少的,那时最富有的人所拥有的物质财富还不如工业化社会中穷人的财富多。在中世纪,即便是至高无上的国王也缺乏基础的娱乐设施,而在今天的美国,中央空调、室内管网以及冬天里新鲜的蔬菜等几乎是人人都能享受的。尽管贝克和查理认为每天吃两条鱼简直奢侈到了极点,可在我们看来,这种生活丝毫不值得羡慕。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财富是分等级的,这个事实本身就不公平。人们认为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攫取别人的财富,并由此产生了穷人。在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理论认为,利润是通过少付工人工资产生的,有人称之为 “劳动价值论”。这样看来,像艾伯这样的企业家或类似的大型公司要想致富,只能先让别人变穷。
上述理念与道德取舍息息相关,但与现实无甚关联。富人致富的原因(至少开始时)是他们为他人提供了有价值的东西。艾伯就为那些没有足够储蓄的人提供了储蓄。如果他赢利了,那也是因为他提供的服务对别人是有价值的。
如果艾伯是一个无赖,每天所做的就是窃取邻居一半的劳动成果,那么他的财富就是建立在那些受其压迫的人的贫穷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做法会迫使他人做一些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情,不会增强这座小岛的整体生产能力。艾伯可能会直接拿走别人生产的东西,而岛上的产量并没有任何变化,不仅如此,他们的整体产能还可能下降。当被压迫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劳动果实被人偷走时,就会缩减自己的劳动量。
历史上,此类事例并不少见,奴隶制、农奴制以及佃农制都属于这一类型。当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劳动者就会奋起反抗压迫,如果他们的劳动惠及自身的话,这种反抗会更加强烈。
不幸的是,争取充分经济自由的实例在世界历史上还很鲜见。不过,一旦利己主义得到发展机会,生产能力就会迅速提高。
信用卡的使用就是经济自由惠及百姓的最佳例证。只要贷款人和借款人可以自由地达成协议,总体效果就是好的。然而,我们将来会发现,借贷市场会受到外力挤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灾难便在所难免了。
第三章 信用貸款的多種用途→信用供給
如果貝克和查理不提高自己的生產能力,他們又怎麼能連本帶利地歸還借款呢?在休息幾天之後,他們還是每天只能捕到一條魚。為了還艾伯的魚,他們以後每天就要減少自己的食量,他們將不得不降低自己的生活水準以償還貸款!
如前所述,艾伯决定把鱼借给贝克和查理,这样他们两个人就可以编织渔网了。这种商业贷款是资本的最佳用途,因为这样可以扩大生产。
当然,通过借钱或借鱼的做法创业,无法保证企业一定会成功,因为借款人可能无法完全实现自己最初的计划。
也就是说,查理和贝克如果不能成功地编织出自己的渔网,艾伯借出的鱼就打了水漂。
在很多案例中,企业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事先应当做好所有约定。假设贝克和查理不是向艾伯借鱼、省出时间来织网,而是利用这些时间研发对鱼群实施催眠术的技术,情况可能会大不相同。
如果他们研发的技术无效,这项贷款就无法使 “借款人” 查理和贝克受益,而贷款人艾伯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最糟糕的情况是,贷给不赢利企业的那些款项浪费了社会储蓄,降低了生产力。结果,贷款人连本金都很难收回,更不要说利息了。
但是实施顺利的商业计划弥补了那些实施不利的计划的损失。
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知道商业贷款并非社会储蓄的唯一选择,艾伯还可以选择其他贷款形式 —— 消费贷款和应急贷款。
故事引申
一旦外部力量(比如政府干预)以各种理由鼓励或者要求储蓄者借出款项,而不考虑实际还款的可能性,这时贷款人就难免要承受较大的损失。这种有悖常规的做法只会浪费社会储蓄。
各国政府满腔热情要做点儿好事,总想干预储蓄的借贷方式。它们通过诸多法律,使得某些贷款类型比其他类型更有吸引力。但是,政府并没有储蓄,只有个人才有!假如在政府的激励之下,贷款都流向了那些最终无法还款的个人或者企业(它们的确经常无力还款),那么这些损失就要由那些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创造储蓄的个人来承担了!
事实上,如果艾伯是被迫向外贷款,而他又认为这份贷款颇有风险,比如用于鱼类催眠术之类的情况,那么他一开始就会很不情愿这样做。因此,他可能会决定不再那么努力地工作,或者不再牺牲那么多去储蓄了!
……
故事引申
遇到经济可能收紧的情况时,政治家和银行家常会讨论是否需要 “扩大信贷”,增加可以借出的贷款数额。但是是否可以随心所欲地这样做呢?在我们这些捕鱼的朋友的案例中,艾伯合法地借出的鱼不会多于自己所储存的鱼,这座小岛的贷款总额会受到岛上所储存的鱼总量的制约。
现实链接
不幸的是,为了开展许多政治家和社会理论家眼中的有益活动,政府总会通过各种形式干预储蓄的配置,包括政府贷款担保、公司及个人税收减免以及税务罚款等。
有了这些干预手段,个人与企业也许更愿意申请某些类型的贷款,而银行也更愿意批准这些类型的贷款。于是,更多的社会资源便会投入这些受欢迎的活动中,比如住房建设、大学教育以及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
这些政策的关键推动因素就是认为政府规划者要比储蓄者更清楚什么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观念。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事实就是这样。实际上,历史上充斥着各种浮夸的政策与方案,这些方案都是政府智囊团策划的,最终全都没有兑现它们的诺言。
更重要的是,政府介入储蓄者和借款人之间采取的强制手段将借款的原因与结果割裂开来,使得储蓄的分配效率极为低下。
影响个体贷款人的往往是贷款的财务结果,而不是基本活动的政治象征意义。而那些遵循成功模式并由业绩记录良好的所有者经营的企业,还贷率往往较高。因此,这种类型的企业规划更容易吸引贷款人。这与达尔文的观点相似,即自然选择催生了生命力更强的物种,这种借贷原则催生出更加健康的企业和更加强劲的经济。
如果财务状况被视为次要因素,这种情况也就不存在了。贷给个人或者企业的款项如果无法成功促成必要的创新或者提高产能,就会浪费储蓄的供给,削弱整体经济。
但我们在本书后面的内容中会发现,不断扩大货币供应量的做法以及政府看似无限的负债能力掩盖了一个事实 —— 实际信贷是受有限储备制约的。
现在,人们都认为信贷市场的有效运作所需要的就是有意愿的借款人。然而,与其他资源一样,在发放贷款前必须先积累储蓄才行。
第四章 經濟到底是如何發展的→經濟效益:儲蓄大於消費
近年來經濟學家們嚴重低估了儲蓄在經濟價值鏈中的位置;事實上,在很多經濟學家看來,儲蓄就是一種累贅。凱因斯主義者認為儲蓄對發展不利,因為這種做法妨礙了貨幣流通,降低了消費(他們認為消費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
考虑到这些问题,贝克决定提议创立一家合伙公司,即三个人共创一家公司,克服暂时的困难,集中他们所有的储蓄,拿出整整一周的时间建造这个巨型捕鱼器。
听了贝克的计划后,他们开始讨论其中的潜在风险。跟艾伯的第一张网一样,没有人能保证这个计划一定能成功。即便计划成功,那个新发明的玩意儿第一次入海时也很有可能被海浪冲得支离破碎。而且这一次他们的风险可不是损失一条鱼,而是 20 多条!
然而,他们对更多鱼的需求最终战胜了对失去全部储蓄的担忧。
三个人向着目标前进。
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建成了小岛上第一个巨型捕鱼器。这个设备果然不负众望,平均每周能捕到 20 条鱼,而且毫不费力。除了几次小修小补和维护之外,这个捕鱼器几乎是在自动工作。很快,三人便拥有了大量的鱼。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岛上的储蓄迅速增加,于是三人很快又建了一个巨型捕鱼器。
【评论:这里数字显然存在问题,因为三人每周需要消耗 21 条鱼,最初只有一个巨型捕鱼器,平均每周能捕到 20 条鱼,这不能使「三人便拥有了大量的鱼」。】
故事引申
储蓄不只是提高个人消费能力的手段,还是防止经济受到意外因素影响的重要缓冲器。
如果一场季风横扫小岛,把两个巨型捕鱼器摧毁了,他们该怎么办?尽管很多当代经济学家将自然灾害视为经济的刺激因素,但实际上洪灾、火灾、飓风和地震等灾害会破坏财富,降低生活水平。如果巨型捕鱼器被彻底毁掉了,小岛上的捕鱼量就会下降,那么艾伯、贝克和查理就又要忍饥挨饿地储蓄鱼以重建资产了。
但是,请记住,一笔备用的储蓄会防止经济崩溃,可以迅速重建受损的资产。艾伯、贝克和查理三人继续缩减消费进行储蓄的做法非常重要,此乃未雨绸缪之举。
现实链接
过去,美国以储蓄大国而著称。在历史上,美国居民每年都会将收入的 10% 甚至更多储蓄起来。这种严格自律的做法帮助美国建立了巨大的储蓄供应,为不断推进的工业活动提供了金融支持,同时也帮助美国的家庭和社区克服意外的困难。
然而,近年来经济学家们严重低估了储蓄在经济价值链中的重要性。事实上,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储蓄就是一种累赘。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储蓄对发展不利,因为这种做法妨碍了货币循环、降低了消费(他们认为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政策制定者们受这些观点影响,制定出各种规则奖励花钱的人、惩罚存钱的人。
结果,美国人多年来总是入不敷出。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中,比如小岛经济,这样做根本不可能。但是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货币流通跨越国界,而印钞机似乎具有无限魔力,可以欺瞒美国民众,让他们无法认清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的消费不能超过产能,我们的借款不能超出存款,至少不能长期这样。
当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条件反射式地寻求各种方法,让消费者花得更多、存得更少。
他们的做法只能适得其反,为了消费而消费的做法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花了 100 万美元,除了空气之外什么都没有买到,那会怎么样?对社会有什么好处?这笔交易只会使出售空气的人受益,他会把原本属于你的那 100 万美元拿走。用现代的经济核算方法计算,比如以 GDP 衡量,这笔交易会被当作一次真实的经济活动,会被算作价值 100 万美元的增长。
但是购买空气的做法不会推动经济增长。空气一直都在那儿。我们必须生产出什么东西,才会使消费有价值。
消费只是我们用来衡量生产的尺度,因为所有生产出来的东西最终都是用于消费的。那么消费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只要价格降得足够低,即便是没人想要的东西也可以卖出去。但是,如果没有生产,也就没有东西可消费了。因此,生产是有价值的。
储蓄创造了资本,而资本使生产扩大成为可能,所以储蓄起来的一美元对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要大于消费掉的一美元。对于这一点,你不必费力向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家解释。
第五章 在魚被指定為貨幣之後→效率、通貨緊縮
很快,所有的工資和價格都開始用魚計量。因為人們仍然假設每天需要吃一條魚才能生存,所以一條魚的價值是多少,所有人心裡都有數,也就是說,島上的價格體系和魚的真實(或者固有)價格相關。
……
生产率提高意味着这座岛屿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反过来,更多的人又促成了更加多样化的经济。……
……
为了改变这种杂乱无章的交换系统,岛上需要新的交换物。这种交换物应该能用来交换任何物品、能被所有人接受。换句话说,岛民需要货币。
鉴于岛上的所有人都吃鱼,鱼被指定为货币。
很快,所有的工资和价格都开始用鱼计量。因为人们仍然假设每天需要吃一条鱼才能生存,所以一条鱼的价值是多少,所有人心里都有数。也就是说,岛上的价格体系和鱼的真实(或者固有)价格相关。
效率与通货紧缩
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工人们有所分工,从事不同的商业和服务活动,其结果一定会比所有人都做同一种工作要好。分工增加产量,高产量又能提高生活水平。
……
由于生产率提高了(储蓄、创新和投资的结果),独木舟的价格便随之下降,更多顾客能够享受到拥有独木舟的好处。昔日富人独享的奢侈品也成了普通消费品。
故事引申
正如故事中所讲的那样,价格下降并没有损害达菲的利益。实际上,其他行业生产的产品的价格也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达菲可以用赚得的鱼买到更多的东西。
技术创新是个单向的过程。除非人们失去记忆,否则生产效率必然会越来越高。因此,价格具有随着时间推移而降低的趋势。
持续下降的价格还会鼓励岛民储蓄,因为他们知道现在的鱼将来会更有价值。尽管听起来可能有些疯狂,不过省一条确实等于赚一条。这样一来,人们就愿意储蓄,也就有更多资本可用于贷款、资本投资、生产,最终带来更多消费。
就业
由于社会发展得更加复杂,越来越多的岛民决定为别人工作,以劳动换取报酬。
劳动的价值通常取决于劳动者所使用的资本。资本越优化,劳动的价值就越大。例如,付出同样的劳动,你驾驶一辆推土机挖的坑要比你用铁锹挖的坑大得多。所以,最好利用可用的最优资本工作。
故事引申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最低薪资法规增加了低端工人的薪资,但实际上,这类法规只是增加了这个人群的求职难度。如果一个员工能够提供具有一定价值的服务,比如每小时价值 8 美元,那么不管有没有最低薪资的规定,雇主都会心甘情愿地支付这笔费用。法律不需要对薪资负责,需要对此负责的是员工本人。但如果这位员工只能提供每小时价值 6 美元的服务,那么在 8 美元的最低时薪规定下,这个人想谋得一份工作是极其困难的。毕竟,没有哪位雇主愿意亏钱雇用员工。这样一来,最低薪资法规使得低技能员工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就业这件事就好比爬梯子,如果没有机会踏上第一级梯档,那些低薪资的员工也就无法获得继续向上攀爬所需的技能了。这一现状使许多人陷入生活拮据的窘境。那些将 6 美元时薪视为剥削的人在为自己的正义感而沾沾自喜,但诸位想一想,在时薪 6 美元的情况下就业总好过在时薪 8 美元的规定下失业吧。
许多政客还喜欢自我标榜,认为自己促成了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因为他们通过各类法规,要求雇主为员工提供强制休假、医疗保健、请病假以及休产假等各类权益,于是便居功自傲。但是在最低薪资制度下,使这些权益得以实现的是员工的生产力,而非那些法规。然而,这些要求却剥夺了员工的选择权:他们本可以在这些权益和更高的薪资之间做出选择,如果那些政客不强制雇主为员工提供上述待遇的话,他们是有可能拿到更高薪资的。诸如此类的规定,外加其他由雇用或解雇员工导致成本及法律风险增加的规定,只能导致越来越多的低技能劳动力漫天要价,从而把自己赶出就业市场。
【评论:对于好吃懒做的无产阶级,最好鼓励它们强调自己无才无德,从而使其不被资本家剥削(被驱逐出就业市场)。】
在自由社会中,所有居民都能判断哪些资本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价值。除了那些出于某种原因依然选择徒手捕鱼的人以外(也许是出于艺术上的原因),每个劳动者都有三种选择:
-
省吃俭用,自制渔网。
-
贷款购买渔网。
-
为有渔网的人工作。
鉴于选项一需要饿肚子,选项二需要担风险,大多数劳动者会选择选项三。他们只需给人打工,就能得到报酬。
……
将来某一天,芬尼根可能储蓄足够多的鱼,制造自己的运鱼车,进而和他的老东家竞争。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莫里不得不支付给芬尼根合适的报酬,比他自己干赚得多,但不会多到让他产生自立门户的想法。
虽然大家都得到了好处,但莫里唯一的动机是追求更高的利润。他并不是有意帮助芬尼根,但他的行为产生了这种效果。结果是芬尼根得到了更高的工资,所有人都降低了运费成本。
有人认为商业利益源于降低员工的薪资。但没有人会免费工作,没有利益,工作也便无从谈起。员工只要工作就有报酬,而企业主想得到回报则只能等到企业赢利,他们的收益是对承担风险的回报,也是对成功整合稀有资源的回报。对利润的不懈追求推动了产品创新、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正是这样的推动力提高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丰厚的利润正说明一个企业很擅长满足客户的需要,对这样的企业应当予以鼓励,而不应恶意诋毁。
故事引申
有人认为,就业市场本身就有失公平,政府需要保护员工免受雇主的剥削。这种想法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存在误解,严重损害了劳动力市场的健康运行。
与自由社会中的任何交易一样,就业是一项自愿的活动。如果人们通过自食其力或受其他雇主雇用能够挣到更多的钱,就很少有人愿意接受或继续一项工作了。每个工作的人实际上都在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将自己的劳动力卖给出价最高的雇主。有时(拿自由的水池清洁工来说),他们将劳动力卖给不同的顾客;有时(就大多数工作者来说),他们只将劳动力卖给某一个顾客,即他们的雇主。水池清洁工能够自由选择,为出价更高的顾客工作(或者在他掌握了新技能后,转行做报酬更高的服务工作)。同样,上班族如果有机会,也可以跳槽,去追求薪资更丰厚的工作。上班族没有跳槽,就证明他们目前的工作可能是当前所拥有的最好选择。低报酬可能不尽如人意,但这并不意味着剥削。
一名员工的具体价值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需求(雇主是否需要这名员工所掌握的技能)、供应(有多少人具备这些技能)以及生产力(这名员工对那些任务的完成程度如何)。要想获得较高的薪资,这位员工必须提高其自身价值,要么掌握极少数人具备的急需技能(如医生),要么通过对本职工作精益求精来提高生产力,根本无捷径可走。
现实链接
对通货紧缩的完全妖魔化(还有对通货膨胀的相对接受)是当今经济学中最成功的宣传策略。在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眼中,通货紧缩被定义为一段时间内价格的全面下降,就好像经济领域的鼠疫一样。只要有一丁点儿通货紧缩的苗头,政府通常就会采取措施抬高物价。
价格下降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已经习惯了不断上涨的物价,要是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将近 150 年(从 18 世纪末一直到 1913 年)中,美国的物价一直在稳步下降,几乎所有人都会大吃一惊。然而,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几个阶段。
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正如本章所讲述的那样,是因为生产率的提高。如果货币供应稳定(就像美联储成立前的美国那样),生产率的提高会促使价格下降。
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工薪阶层也能买得起装饰家具、量身定做的衣服,付得起水管维修费和乘车费,而这些以前只有富人才消费得起。通货紧缩意味着 1850 年时存下的 100 美元到了 1880 年能够购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为什么说通货紧缩不是件好事呢?现在,爷爷奶奶总爱说他们小时候东西多便宜,而他们的爷爷奶奶却总是说自己小时候东西要贵得多。
虽然物价低的好处显而易见,但我们还是害怕通货紧缩。我们被告知:一旦物价下跌,消费者就会停止消费,公司也会避免支出,工人会因此失业,最后我们会回到经济的黑暗时代。
但是,价格下降并不一定会影响特定行业的发展,我们不止一次地见证过这一点。20 世纪初,亨利・福特靠不断降低汽车的价格发了大财,他雇用的工人的工资是行业里最高的。举个更近的例子,虽然计算机的价格不断大幅下降,但是这个行业的赢利还是非常丰厚。产品价格的下跌并未阻挡计算机革新的步伐。由于设计和制造效率的提高,每年有数亿人能够以越来越低的价格享受数字化带来的好处。
尽管如此,大多数人都认为通货紧缩只有在局限于某个行业时才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呢?
现代经济学错误地认为: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因而一旦发生通货紧缩,人们就不愿意消费(这样价格就会继续下降),而如果人们继续消费,价格下降的影响就会减弱。真是荒谬。
正如我们前面讲的那样,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消费,而是生产!
不需要劝说人们消费,因为人类的需求永远不会得到满足。如果人们不想要某样东西,那一定是有理由的,要么是产品不够好,要么是买不起。不管是因为什么,推迟购买产品,或者把要花的钱存起来,都是出于理性的考虑,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有好处。
实际上,如果消费者不愿意消费,刺激需求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物价降到更合理的水平。山姆・沃尔顿就是运用这个简单的概念赚了数百亿美元。
第一代等离子电视问世时,极少有美国人购买。尽管大家都想要一台,可一万美元的不菲价格却令许多人望而却步。但价格下跌时,越来越多的人果断出手,争相购买。不断增加的销量弥补了价格下跌带来的损失,于是利润大幅提高。
天资敏锐的经济学家总会说,价格下降会损害众多消费者的利益。可食品与能源价格降低真的很糟糕么?医保花销或者教育投入逐渐回到可承受范围内,难道我们还会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以规避相关风险么?
虽然有这么多反面证据,通货紧缩还是被当作经济的头号敌人。这是因为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相反)是政治家最好的朋友。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说明。
第六章 為什麼會有儲蓄→經濟崩盤的前兆、低利率的影響
有時生產率大幅提高,島上的存魚量也隨之大大增加。如果儲藏室裡堆滿了魚,銀行就會主動降低貸款利率,不只因為此時銀行承受損失的能力較強,也因為現在這個有能力創造更多儲蓄的健康經濟體為新企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随着岛民储存的鱼越来越多,鱼的存储成了问题。以前,人们习惯把鱼存放在家里,但是这样做效率很低甚至很危险。偷鱼贼也成了一个大问题。
虽然岛民愿意通过贷款和投资使自己多余的鱼增值,但是大多数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判断某项商业计划的优劣。
一个名叫 “迈克斯・郝寅航”(Max Goodbank)的人嗅到了商机,他决定开拓一个革命性的行业。
迈克斯守护自己的存鱼多年,深知必须找到一种更好的储存方式才行。看到自己的邻居被狡猾的借鱼者欺骗,他也认识到大多数人在借出积蓄的问题上都需要帮助。考虑到这些因素,他建造了一个很大的储藏室,其温度和湿度都可以调节,还雇用了岛上最强壮的人看守。这家新 “银行” 能够确保岛上存鱼的安全,从而解决存鱼失窃的问题。但这只是个开始……
迈克斯是位真正的企业家,他知道如果只是收取保管费,利润空间很有限。
他明白储蓄的价值,也明白自己比一般的岛民更擅长放贷。迈克斯是一流的数学家,尤其善于评估商业计划并为之提供适当的贷款。
他用邻居的储蓄放贷,所获收益的一部分作为储户的利息和看守人员的工资,剩下的部分作为自己的利润。
于是郝寅航存贷款公司就这样诞生了。
与艾伯和达菲一样,迈克斯最初只是想为自己谋利。但是在他追逐利益的同时,也解决了存款、贷款和盗窃这些棘手的问题。
现在,岛上的居民们节衣缩食,把积蓄存入迈克斯的银行,让他替自己承担投资的责任。
谁要是有投资项目需要贷款,只要去找迈克斯就可以了,不用去找那些可能拥有大量存鱼的人。
要让计划顺利实施,迈克斯需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他必须保证贷款业务赢利,这也就意味着他必须仔细甄选合适的借款人,认真收取利息,而且当对方无法还款时取消抵押品的赎回权。
第二,他需要定期向储户支付利息,让他们高兴。第三,为了让生意持续下去,他需要吸引更多的储户。如果失败,他就会失业,他的投资也就白费了。
因为迈克斯精通贷款业务,凡他经手的贷款不仅效率高,而且利润丰厚,所以他自然而然成了岛上的经济权威。其他不够专业的岛民总会受到个人经历、家庭关系和情感的影响,迈克斯却可以心无旁骛地关注经济问题。
利率
由于迈克斯的个人利益和银行的经营状况密切相关,他最适合决定存款和贷款的利率。
在贷款方面,他对最可靠的(还款能力最强的)借款人收取最低利率,对风险较高的借款人收取较高的利率作为高风险的补偿。
贷款利率又决定了银行能支付给储户的利息。存款利率是随存款年限递增的。存款年限越长,造成银行存鱼短缺的风险越低。因此,如果储户愿意长期储蓄,获得的利率也就较高,进行短期储蓄的储户所获利率则较低。
尽管迈克斯掌握着利率的制定权,但是整体利润还是会随着无法掌控的市场情况的变化而波动。
有时生产率大幅提高,岛上的存鱼量也随之大大增加。如果储藏室里堆满了鱼,银行就会主动降低贷款利率。因为此时银行承受损失的能力较强,而且健康的经济也为新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由于不需要吸引新的储蓄,贷款利率也比较低,这就导致存款利率降低,从而抑制储蓄。
一旦储蓄回落(这对经济来说很危险),相反的力量就开始发挥作用,鼓励储蓄,从而补充银行的资产。
当存鱼较少时,迈克斯放贷就格外谨慎。因为在储蓄不足的情况下,一旦有人拖欠贷款,后果将非常严重。为了抵消高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迈克斯会向借款人收取更高的利率,并提高存款利率以刺激储蓄。
高利率会抑制借贷,延缓经济增长。但同时,高利率也能刺激储蓄。最终,银行资产会再次积累起来,到那时利率又会下降。
另外,较低的存款率表明人们更愿意将储蓄用于近期消费,因而抑制了为满足未来消费需求而进行的投资。
这种周期性的利率机制有利于市场稳定。该机制的运作完全取决于以下三点:银行实现资产回报最大化的愿望、银行对高风险投资损失的担忧、个人消费的时间偏好。
更重要的是,银行储蓄的安全与便捷促使人们增加储蓄、延迟消费,从而为投资项目提供资金,有助于增加未来的产量并提高生活水平。
在迈克斯精明谨慎的经营之下,岛上的储蓄不断增长,商业不断发展。
高风险投资
由于迈克斯需要不断向储户支付利息,他往往会避免发放违约风险较高的贷款。他拒绝发放度假贷款、消费贷款以及其他仅用于消费享乐的贷款。这类借款人总是夸下海口,却拿不出实际的证据证明他们将来能够还贷,所以迈克斯不能拿岛民的储蓄冒险。
但是,有些储户甘愿为了高回报承担高风险。偶尔会出现一些有潜在突破性的项目,非常诱人,但是最后银行还是因风险过大而不愿投资。
弹射飞行航空公司提出了一个设想,可能会彻底改变岛际旅行方式。
但是,循规蹈矩的迈克斯不肯投资。
然而,这并不表示弹射飞行的支持者束手无策了。
一个新的联合投资组织出现了。该组织由阔绰的大亨曼尼・季金(Manny Fund)运营。曼尼从那些对银行存款利率不满意的储户那里募集存鱼,然后再把募集到的鱼投入备受瞩目的项目。
有些项目成功了,比如天堂饮品公司。
另一些项目则失败了,比如布拉潜艇水下旅游公司。
迈克斯继续通过保守的投资方式促进资本增长,而曼尼则成了冒险者的选择。
现实链接
政府不但制定法律,向某些贷款类型和人群倾斜,扰乱了信贷市场,还通过另一种更加根本的方式影响信贷流动:操控利率。在将近 100 年中,美联储(理论上是一家私有银行,但实际上却是美国财政部的延伸)一直制定基准利率,而美国的整个利率结构就是建立在基准利率之上的。
美联储调高或调低联邦基金利率并不会直接决定某家银行每种贷款的利率,但会影响整个市场走高或走低。通常,银行向大众收取的利率要高于它们支付给美联储的贷款利率。因此,当美联储调高或调低其基准利率时,企业和个人在借贷时就要多付或者少付一些钱。
美联储之所以被授予这一权力,是为了保证经济不论在繁荣期还是萧条期都能平稳运行。其理论基础是: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可以运用集体智慧,推算出特定时段最理想的利率水平,从而使经济正常运行。
例如,美联储可以把利率降到足够低,这样企业和个人就更愿意借贷,以此刺激不景气的经济。而在经济繁荣时,由于过分的自信经常导致愚蠢的行为,美联储应该提高利率,这样人们在借贷时就会三思而后行。
这个机制有两个致命的缺陷。
第一,该机制的前提是:美联储的一小撮人要比数百万独立决断的民众(或者叫 “市场”)更清楚什么是恰当的利率水平。但是,美联储跟利率没有任何关系。它既不产生储蓄,也不会因为贷款变成坏账而蒙受损失。积累储蓄的是民众,而且银行能否获利取决于自身的管理水平。如果没有这种关联,借贷必然是低效的。
第二,美联储的决定总是基于政治考量而非经济因素。因为低利率能够使经济表面上表现更好,降低还款压力,还能帮金融公司赚钱,所以很多人都喜欢低利率。谋求连任的总统往往鼓吹更低的利率,并对美联储施压。对于美联储的决策者来说,他们自然也希望自己被看作拯救经济的好人,而不愿被当作将经济推向低谷的吝啬鬼。
乐于看到高利率的社会成员(尤其是储户)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没人听取他们的声音。因此,社会上就形成了这种偏见,即利率应该很低,而不是很高。但是要记住,低利率会刺激借贷、抑制储蓄,难怪美国已经由一个储蓄者的国家转变成了借款人的国家。
而且,相对于储蓄供给来说,过低的利率会向借款人传达错误的信号,即经济状况良好、投资可行。因为消费并没有真正延后(如果利率顺应市场下滑,消费就应该延后),用于满足未来需求的投资就很难成功。结果就是虚假的繁荣过后紧接着出现巨大的危机,正如我们刚刚在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上经历的那样。
第七章 基礎建設與貿易→建設是成長或浪費?
隨著島上經濟的發展,出口產品的能力也增強了。很快,不少大型貨運木筏就滿載著魚、運魚車、衝浪板、長矛和獨木舟駛過公海。
故事引申
现在岛上的社会比当初只有三个人徒手现在岛上的社会比当初只有三个人徒手捕鱼时要大得多了。在一些人看来,支配经济的原理已经改变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正如数学原理不会因问题的大小而改变,基本经济原理也不会因经济的大小而改变。人们常常认识不到这一点,是因为在储户和借款人之间存在着很多层关系。但是,自我牺牲、储蓄、借贷、投资、经济刺激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永远不变的。
贸易
随着岛上经济的发展,出口产品的能力也增强了。很快,不少大型货运木筏就满载着鱼、运鱼车、冲浪板、长矛和独木舟驶过公海。由于物美价廉,这些产品在整个大洋上都享有盛誉。人们用它们换取了鲜鱼和其他以前从未在小岛上见过的商品。
由于岛上的探险者和其他岛屿建立了联系,贸易得到了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如果自由贸易不受限制地自由发展,就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
有些岛屿(或者城市、国家甚至个人)通常会有一些产品相对过剩,而别的岛屿正好缺乏这类产品。于是,每个人、每个国家或者岛屿都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实现利益最大化。
……
国际贸易与个人劳动分工没有什么区别。每个人或者每个国家都用自己多余的或者擅长生产的产品,换取自己缺乏的或者不擅长生产的产品。
现实链接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只有在收益大于支出时,这种投资才有效果。反之,这些项目就是在浪费资源并阻碍经济增长。
目前,很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错误地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并不是可能带来长期收益的投资,而是增加就业和提振经济的直接手段。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远远不够。弥补这个缺口对于目前的经济状况而言无疑是一种负担。我们将来才能看到这些投资的收益,而且前提是投资必须成功。
在我们的故事中,借给自来水厂项目的 182 500 条鱼就不能再用于其他能够创造就业岗位的投资项目了。其实那个机会不错。假如这些鱼被用在了一个毫无价值的项目上,比如阿拉斯加臭名昭著的 “绝路桥”,那就浪费了岛上的储蓄,白费了 250 名工人两年的辛勤劳动。
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上,类似自来水厂这样的项目往往是由私营部门发起的。然而,由于这些项目能否成功很难预料,在这个政府几乎控制了一切基础设施建设的时代,这样一个工程的融资、建设直到最后投入运营都由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公司完成,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是在过去事实就是如此。
举例来说,纽约地铁基本上就是由私营公司建设的,而且在近 40 年的时间里都是由私营公司负责运营。虽然地铁的造价不菲,但还是实现了赢利。更值得一提的是,40 年里车票价格从未上涨。
现如今,选民很容易相信大型公共设施都应该由政府运营,比如下水道、高速公路、运河和桥梁这些可以为所有人提供方便的设施。
政治家们成功地让民众相信,唯利是图的私营公司一有机会就会榨取民众的血汗钱。他们用来证明这些论点的证据多半都是从情感上煽动,引起民众的共鸣。其实我们更能确定的是,政府对于公共设施和服务的垄断几乎必然会造成效率低下和贪污腐败。
如果政府工程入不敷出且服务质量很差,自由市场的原则也无法帮助其走出困境。政府通常会通过提高税收填补漏洞。这样一来,不仅浪费了社会资源,也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在贸易上,人们也有同样的错误理念。自由贸易的反对者试图保护美国的就业岗位不受海外竞争的影响,但是他们忽略了进口的好处,忽视了限制选择范围对消费者造成的潜在损失。
比如,如果进口的 T 恤衫比美国本土生产的 T 恤衫便宜,那么美国人就可以在 T 恤衫上少花一些钱。省下来的钱可以用于生产别的东西,比如滑板。这对于美国国内的公司,比如优秀滑板制造商,是很有利的,对那些能够输送其最有价值产品的公司也是有利的。
可是美国国内那些制作 T 恤衫的失业工人怎么办呢?如果他们的雇主不能在生产 T 恤衫上找到竞争优势,这些工人只能去找别的工作。但是,提供就业岗位并非经济的目的。经济的目的是不断提高生产力。
保留无效率的劳动力和资本使用方式对整个社会是没有好处的。如果美国在 T 恤衫生产方面没有竞争优势,那么它就应该找到自己具有优势的行业。
如果通过贸易壁垒保护这些就业岗位,制造 T 恤衫的成本还是会居高不下,那么人们就没有更多的钱购买滑板(举例来讲),滑板制造商就会蒙受损失。所以,这种做法虽然保留了上述就业岗位,但我们却没有看到那些因此失去的潜在岗位。
浪费劳动力制造那些国外生产率更高的产品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专注于生产自己擅长制造的产品,就可以用它们换取别人擅长制造的产品,最终能得到更多。
当然,问题在于,因为有了那些人为设置的高汇率、高税率,以及工资法和劳动法,美国占优势的领域并不多。这个局面需要改变。
第八章 一個共和國就這樣誕生了→權力、自由、約束
為了維護社會穩定,也為了保護島民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參議院決定設立一套法院體系來解決糾紛,同時成立員警小隊執行法官的法令。
……
故事引申
岛民们知道政府的支出就是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所以他们认为应该由纳税人决定税款怎么花。因此,只有纳税人可以投票。
岛民们也明白税收降低了岛上可用的储蓄总额,限制了投资资本的供给,但是大多数岛民都认为更安全的环境、船只失事事件的减少和解决合同纠纷的法院系统所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他们所付出的代价。
目前为止,一切都好。但是总会有些事情发生……
现实链接
美国建立在对政府权力严格限制的基础上,但是很遗憾,很少有美国人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对盛行于 17~18 世纪的关于自由、理性和科学的革命性思想了然于胸,他们试图在人民与政府之间营造一种崭新的关系。在他们的设想中,主权在民,人权神圣不可侵犯。
独立战争结束之初,为了建立国家政权(其实很多美国人并不希望这样),美国宪法成了一个设计巧妙的笼子,可以防止政府这个 “野兽” 发狂失控。宪法不仅防止人民免受政府的独裁统治,还防止少数人受到多数人的暴政的伤害。
美国宪法有意将权力分配给联邦政府的不同部门,并把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各州。更重要的是,宪法可以防止联邦政府从人民手中剥夺任何权利。
结果,在这个国家里,人人可以享有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个人资产,政府无权干涉。虽然并非每个人都能幸运地享有这些权利,但是这无损于这个设想展现出的勇气。毕竟,这是以前任何国家的法典中都不曾有过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清晰的设想变得模糊了。危机爆发时,很多人都确信政府需要更多权力,人们可以牺牲一些自由。不幸的是,在目前的经济危机中,这个想法仍有不少支持者。
我们渴望消除经济紧缩带来的痛苦,但是我们忘记了自由本身就是有风险的。如果政府有责任消除一切苦痛,那么就没有人是自由的。无法自由地失败,也就是无法自由地成功。
第九章 政府的職能開始轉變了→發行魚券
因為只需要少數熟練的漁民捕魚便可以滿足整個島嶼的營養需求,多出來的勞動力和資本就可以投入其他行業了。各種在捕魚時代聞所未聞的工業和服務業都發展起來。
在 几代人的时间里,岛上的政府一直按照设想运行。很多睿智而又严于律己的人做过领袖,他们一直十分注重鼓励企业发展和个人储蓄。在此期间,税收负担相对较轻,对行业的管制也比较宽松。随着商品生产的增加,企业获利,价格稳定回落,购买力增强。在几代人的努力之后,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拥有一条独木舟,有些家庭甚至有两三条。
因为只需要少数熟练的渔民捕鱼便可以满足整个岛屿的营养需求,多出来的劳动力和资本就可以投入其他行业了。各种在捕鱼时代闻所未闻的工业和服务业都发展起来。棚屋装修公司、巫医医院和制鼓公司应运而生,蓬勃发展。岛上一片繁荣。西海岸还出现了一个剧团,人们对他们的首场演出《渔民来了》赞不绝口。
与此同时,一些参议员基于情感原因认为,宪法中关于纳税与投票权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非民主的。基于进步主义精神,这项规定被废除了,很多不太关心政府预算支出的人也获得了投票权。
政府的工资支出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参议员的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这份工作变得非常有吸引力。本来只有德高望重的长者才能担任参议员,现在雄心勃勃、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也对此趋之若鹜。
渴望成为参议员的人当中有个名叫 “弗兰基・迪普” 的人,他比其他人更有创意。他注意到人们做事的一个特点,这为他以后登上权力顶峰提供了途径。
他发现人们喜欢免费的东西,同理,人们痛恨纳税。因此,他想出了一个计划:如果他能找到一个方法让岛民们以为他免费给予了他们一些东西,那么他就能够得到无条件的支持。不幸的是,政府所有的一切都来自税款。参议员自己又不捕鱼,他们如果不索取就没法给予。怎么可能给予比索取的多呢?
一次猛烈的季风过后,弗兰基看到了机遇(政治家从来不会浪费一次危机)。
他鼓吹道:“亲爱的岛民们,我们刚刚经历的风暴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很多人无家可归、饥肠辘辘,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如果我当选,我会制订一个政府重建计划,帮助最需要的公民弥补损失。” 他还向公民承诺,重建的费用由政府税款负担。
他的竞争对手格鲁坡・克利夫兰仅仅承诺要好好管理岛上的储蓄,以及不干涉公民权利。
毫无悬念,弗兰基・迪普顺利当选为议长。
他的胜选并没有改变现状,岛上依然没有足够的储蓄支持他所设想的支出计划。为了弥补这个差距,弗兰基想出了另一个计划。政府可以发行纸币,叫作 “鱼邦储备券”,用这种纸币可以到郝寅航那里自由兑换政府储存的鱼。居民们可以立即把纸币兑换成鱼,也可以用纸币购买产品和服务,就像使用真鱼一样。
……
现实链接
我们前面讨论过,在美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通货紧缩持续存在。1913 年,美联储成立。美联储发行纸币,承诺纸币持有者可以随时将其兑换成黄金,从而取代了当时流通的私营银行发行的钞票。其实,私营银行也做出了相似的担保。但是,自从美联储登上历史舞台,美国的物价就开始不断上涨。
成立美联储的最初目的是形成 “弹性货币供应”。当时的设想是:美联储可以根据经济活动的情况,扩大或收紧货币流通量。设计者以为这样可以让物价保持平稳,不受繁荣或萧条的影响。
即便这一设想是个好想法,很明显美联储在这个任务上已经一败涂地。
在过去的 100 年里,美元损失了超过 95% 的价值。这可真够稳定的!事实上,美联储现在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产生足够的通货膨胀,从而使政府的支出大于税收收入。
在 “大萧条” 中,罗斯福总统决定让美元对黄金贬值。要想实现这一点,美国政府就必须控制整个黄金市场,而且美国政府还一度立法禁止私人拥有金币。后来,要将纸币兑换成黄金,人们只能去公正的银行,后来只能去公正的外国银行,再后来去哪里也兑换不了了。
美国人手里只剩下一种没有实际价值且可以随意增发的货币。这使得美国政府再也不必在支出和税收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也把美国经济引上了一条不归路,总有一天美元剩余的那点儿可怜的价值也会消失。
第十章 不斷縮水的魚就像貨幣一樣→支出 > 儲蓄、通膨問題
官魚越來越小,不久後島民每天只吃一條魚已經無法填飽肚子了,大多數人每天至少要吃兩條魚。
……
参议员们都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现在,他们可以随意做出任何竞选承诺了,再也不必维持收支平衡,也不需要通过提高税率为支出筹钱了。
因此,每年政府都发行数量超过银行中可兑换的鱼的鱼邦储备券。一旦储蓄偏低,技师们就施展他们魔法般的技艺。这一切是如此令人兴奋。虽然参议员们心中痛苦挣扎,想要控制局面,让国家回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但是他们就是无法控制自己。
一些政府拨款支持的项目使大家受益。岛上的海军换了大船,让小鼓岛人无法靠近,新的道路系统使交通更加便利。然而,充满争议的清洗石块就业计划有多大价值就不好说了。岛上到底是否需要闪闪发亮的石头呢?人们的争论丝毫不能降低那些因为这项计划得到工作的人对该计划的推崇程度。
与此同时,新政府渔业部成立并开始运营。渔业部提供很高的工资和良好的福利,很容易就雇到了员工。被雇用的人很喜欢这份稳定的工作,很高兴地把选票投给了他们的参议员赞助人。
但是,在光鲜的外表下面,真正的问题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
由于渔业部的员工不会出于个人利益去冒险或获取利润,所以他们的效率很低下。
……
通鱼膨胀抑制储蓄,银行储蓄额随之降低了。结果,可以用来投资有前景的项目或者支持不景气的企业的存鱼减少了。相应地,企业开始削减成本,很多工人因此失业。很多岛民迫切希望抵消通鱼膨胀的影响,于是他们决定冒险把存款交给曼尼打理,因为曼尼承诺的回报率很高,这是投资者弥补损失的最大希望。
后来失业率达到了危险的水平,人们要求政府采取措施。
于是,参议院严格规定了企业应该向工人支付的最低报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雇用和解雇工人,以及产品价格应该怎么制定。有了这些限制,企业做生意更加困难,发展能力也受到限制。
……
现实链接
经济学家们非常成功地混淆了通货膨胀的起因,手段之一就是简化这个词的定义。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物价上涨就是通货膨胀。因此,如果物价没有上涨,就没有通货膨胀。
但是上涨的价格不过是通货膨胀的结果罢了!这就好比给气球充气,气球就会不断膨大一样。通货膨胀其实就是货币供应量增加,与其相反的情况即为通货紧缩,意指货币供应收紧。从另一方面来说,价格自身其实不会膨胀或者紧缩,只会上涨或下跌。所以膨胀的不是价格,而是货币供应。
凡是 1990 年以前出版的字典对通货膨胀的定义都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较新版本的字典的定义就开始松动了。不过,如果你明白通货膨胀的真正含义,你就会明白,就算货币供应量增加,物价也可以保持平稳甚至下降。
经济不景气时,人们会理智地选择停止消费。一旦这样,需求就会降低,物价就会回落。不过有时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够抵消这些因素,因为增加货币供应量会降低货币的价值。如果通货膨胀发生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物价会上涨(前提是货币发行的速度足够快)、保持平稳或者比正常情况下跌得慢一些。
但是,经济不景气时,物价需要下跌才能平衡经济局势。经济不景气时需要通货紧缩,物价下跌能够削弱低就业率的影响。然而,当代经济学家却认为,物价下跌会导致经济陷入需求崩溃的万丈深渊。他们忘记了一旦物价下跌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会开始消费。这个过程淘汰了不必要的产能,把物价调低到符合内在供求关系的水平。
通货膨胀人为地使物价居高不下,妨碍了上述过程发挥作用。
目前,许多政府应对经济衰退的本能反应便是造更多的货币。但是如果货币投入过多,这种手段就会同时带来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两大问题,导致 “经济停滞型通货膨胀” 的出现。20 世纪 70 年代,这种现象最为突出。然而,现今的许多经济学家却一股脑儿地将 20 世纪那段插曲抛到九霄云外,坚持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根本不可能同时存在。他们认为,人们失业时,需求便会下降,价格也会随之下降,可他们却忽略了等式的另一边:一旦工作的人数量减少了,生产的产品也会减少,供应量便会减少。而物质匮乏会导致价格上涨。如果人们向这种并不明朗的经济状况中投入更多货币,必然会导致价格飞涨。
第十一章 中島帝國:遠方的生命線→國外需求與貿易
現在的情況是民眾失去了信心。如果我們現在開始消費更多的魚邦儲備券,人們的信心就會恢復,民眾就會重新開始消費。如果有必要, 我會坐在棕櫚樹上往下撒錢。
……
这位大使在东部海域发现了一个名叫 “中岛帝国” 的岛国。在那里,所有的居民依然在徒手捕鱼。中岛帝国的经济缺乏自由,因而发展缓慢。
在中岛帝国,所有人都必须捕鱼,然而捕获的鱼却不归个人所有。所有的鱼都要上交给国家,由国家决定谁应该得到多少。
中岛帝国的国王如果注意到他的渔民没有竭尽全力,就会要求他们在打鱼的同时一起唱爱国歌曲。如果有人忘词了或者走调了,不予以纠正就没有饭吃。
在这种制度之下,虽然人均捕鱼量不高,但是当权者却能得到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所以,中岛帝国的一般民众每天只能吃到半条鱼,而国王和官员们却每天都能吃到美味海鲜。
中岛帝国的情况跟美索尼亚国出现第一份资本前的情况很像,那时没有储蓄,没有银行,没有信贷,更没有企业。在美索尼亚人看来,中岛帝国的经济还处于黑暗时代(中世纪水平)。
……
这些交易大大促进了美索尼亚国的发展。一方面,国外需求推动了当地经济;另一方面,中岛帝国存入银行的鱼也使可用的贷款大幅增加。尽管美索尼亚人消费比储蓄多,银行依然有足够的鱼可以拿出来以很低的利率提供贷款。
有了大批的真鱼,官鱼骨头上的肉多了起来,美索尼亚国的通鱼膨胀问题基本消失了。因为官鱼变得比以前大,物价停止了上涨,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再度提高。
中岛帝国也是日新月异。
后知后觉的国王终于意识到了国内经济模式的致命缺点。如果岛民们必须上交所有的鱼,他们永远不会卖力干活。国王想通了这一点,他从美索尼亚国购买了渔网,然后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政策改革。凡是从国王这里购买渔网的人,都可以把多出来的鱼留归己有。毫无疑问,岛上的捕鱼活动活跃起来。
中岛帝国的岛民们非常明智地用他们积攒的储蓄购买了资本设备,扩大了生产。但是中岛帝国的企业家依照国家的要求,生产那些可以兑换成鱼邦储备券的产品。因为美索尼亚国掌握着所有的鱼邦储备券,所以中岛帝国的工厂集中生产美索尼亚国人想要的东西。
有了多劳多得的激励制度以后,中岛帝国很快就积累了不少储蓄,并扩大了生产。结果,中岛帝国的企业家们现在也有能力兴建工厂制造产品了,比如勺子和碗。尽管大多数中岛帝国人自己还缺少这些东西,但他们却把这些货物卖给美索尼亚人。你也许猜到了,这样做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鱼邦储备券。
现实链接
多年来,经济学家对美中关系的理解一直是错误的。大多数人认为那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双边关系:美国得到廉价商品和贷款,中国得到制造业的就业机会。然而,这真的是一种双赢的安排吗?
美国人占了便宜:他们不用生产就可以得到商品,不必储蓄就可以得到贷款。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辛勤工作却不能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他们努力储蓄却得不到贷款。
这有什么好处呢?美国的低利率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外的高储蓄率造成的,大多数当代经济学权威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要记住,想要借贷,就必须先储蓄。所幸,对于美国来说,全球经济使得借与存的关系可以不受国境的限制。
到目前为止,美国手中的王牌一直是美元的地位。作为世界的官方储备货币,美元是一切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美国的贸易伙伴,所有人交易时都需要使用美元。所以,即便没有人购买美国的产品,人们也需要美元。而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这种运气。
外国人持有的美元很多都存在美国的银行里,因而又可以借贷给美国人。这么一来,美国人即使不储蓄也可以获得贷款。
人民币和美元紧密挂钩,这就要求中国公民至少要将储蓄的一部分兑换成美元。
如果没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储蓄,美国人以及美国政府想要借钱就会很困难,他们将不得不承担高额的贷款利率。对于靠贷款推动的美国经济而言,利率偏高和信贷吃紧是一个致命的组合。
目前美国领导人和中国的冲突不断升级,在他们决定与中国划清界限之前,需要好好认清这条生命线。当然,既然这种关系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结束得越早,痛苦就越小,对美国人来说尤其如此。白食吃得越久,有朝一日没得吃时,就越是难以自食其力。
第十二章 服務業是如何崛起的→美元地位、貿易順差
中島帝國攢夠了錢,建造了很多巨型捕魚器(捕魚器的設計者起訴他們侵犯智慧財產權,但是在中島帝國完全沒有勝訴的可能)。他們實行 24 小時工作制,三班輪崗,不間斷捕魚。大部分魚都出口到了美索尼亞國。
中岛帝国的储蓄大量涌入,贷款利率随之降低,这使美索尼亚国企业家们的投资热情高涨。但是,由于捕鱼和制造业的工作越来越多地外包给中岛帝国,他们提出来的商业计划和以往大相径庭。现在,大多数商业计划更青睐那些需要本地员工提供服务的项目。这类工作无法外包,而且需要的资本较少。
在美索尼亚国第一次经济会议上,本・伯南柯为解释这些变化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讲。他认为美索尼亚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捕鱼和制造业这类低级劳动应该外包给穷国,而美索尼亚人则可以自由地从事更加复杂的服务业的工作,比如厨师、演讲家和艺术家。
……
故事引申
与大多数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一样,伯南柯认为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最大的消费群体就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尽情购物要比卖力工作更让人快乐。这一点连傻瓜都知道。但是,是卖力工作的人,而不是尽情购物的人,第一时间将商品放在货架上。没有产品,购买就无从谈起。一旦某个产品被生产出来,它将必然被用于销售。可能发生变化的仅仅是其购买者和价格。
现实链接
过去 10 年里,全球经济失衡是大多数重量级经济会议上常常讨论的问题。虽然人们为此发表了无数的演讲,写过长篇累牍的报道,这个问题却丝毫没有得到解决。
全球经济失衡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在美国历史上的多数时期,出口都大于进口,造成贸易顺差。在有些年份,尤其是接近 20 世纪中叶的时候,贸易顺差额还相当巨大。美国利用这些盈余在国内置办了更多资产,在国外也购买了不少资产。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贸易平衡被打破了。自 1976 年以来,美国开始常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
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贸易逆差的扩大。如果没有全球经济系统对美元的内在需求,任何国家都无法长期维持这种失衡状态。各家公司和各国政府都会拒绝用商品交换无法购买任何东西的货币。
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美国的贸易逆差为 100 亿~500 亿美元,虽然数额巨大,但仍在掌控中。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贸易逆差冲破 1 000 亿美元关口。虽然数额大得惊人,但与美国巨大的经济总量相比,这个缺口相对不大。不过,一进入 21 世纪,情况就变得严重了。
21 世纪的前 10 年是中国作为出口型经济大国崛起的 10 年。在这 10 年里,美国的贸易逆差平均每年都达到 6 000 亿美元,2006 年更是达到了令人咋舌的 7 630 亿美元。这就意味着,每个美国人,不论男女老少,都要分摊 2 500 美元。
幸好,2008 年经济衰退开始后,美国的贸易逆差有所减少。但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的那样,美国的政策很快终结了这种积极的趋势。
正常来讲,贸易逆差能够自我调节。
如果一个国家处于贸易顺差状态,也就是说其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就会在国际上形成对其货币的需求。如果你想要该国的产品,你就需要该国的货币。所以,强势的贸易地位会使一国货币坚挺,弱势的贸易地位会导致该国货币疲软。如果没有人想购买你的产品,也就没有人需要你的货币。
但是,一旦一国的货币升值,该国的产品也会相应涨价。这就给处于弱势贸易地位的国家提供了进入该国市场的机会。他们的商品销售得越多,国际市场对其货币的需求就越大。这股货币平衡力量会使脱缰野马般的贸易失衡得到控制。
然而,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以及中国政府保持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决定破坏了这一机制,使局势越发不可收拾。
近些年来,为了给其出口企业提供一种理论上的优势,多国政府广泛开展多项活动抑制其货币,这些活动引发了人们所说的 “全球货币战争”。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对抗,因为对抗的目的通常不是除掉对手,而是干掉自己。
诚然,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行之有效的销售渠道卖掉更多的产品,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损失部分利润。另外,廉价货币同时也会提高进口成本,因为出口不过是补偿进口的一种方式。一个国家有意弱化本国货币,以此让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来补偿进口商品。这便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会下降。
第十三章 「魚本位」的破滅→再次通膨
頻繁兌換真魚開始對存魚造成衝擊,技師們又忙碌了起來,他們不斷地切割、重組,官魚越變越小,通魚膨脹又有抬頭之勢。
……
里实成功地降低了税收,放松了管制,还减少了与其他岛屿进行自由贸易的壁垒。然而,他减少政府支出的承诺并没有兑现。虽然里实营造了良好的经济氛围,但是参议院的收支差距还在持续扩大。实际上,在里实的统治下,这个缺口越来越大,经济危如累卵。
好在国外的鲜鱼源源不断地涌入银行。用来买鱼的钞票流通到了国外,永远不会再兑换成真鱼。有了这么一个聚宝盆,美索尼亚国进入了表面上看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现实链接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人类曾把各种物品当作货币。食盐、贝壳、珠子和牲畜都曾流通一时,但是,最后金属(尤其是金银)成了最普遍的货币形式。这绝非偶然。贵重金属拥有货币的所有价值属性和使用属性:储量稀少、人人想要、质地均匀、性质稳定、延展性好。
即便人们不想用贵金属充当货币,贵金属依然因为有其他用途和储量稀少的特性而具有价值。
相反,纸币只有在足够多的人愿意使用纸币交换产品和服务时才有价值。因此,纸币的价值完全由人主观决定。由于纸币可以无限量地发行,并且没有内在价值,如果人们对纸币失去信心,它们就会变成一堆废纸。
虽然经济学家声称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切,但事实上,从长期来看,我们并没有预见全球经济会建立在一种不可兑现的货币(通常称之为 “法定货币”)的基础上。“法定”(fiat)一词来自拉丁语,字面含义为 “让它做”(Let it be done)。我们用这个词是想表达纸币本身没有内在价值,是因为政府的命令而具有价值。
历史上不乏失败的例子:某些政府陷入财政困境,走投无路,于是把发行毫无价值的纸币的做法当作救命稻草。这些做法最终往往惨淡收场,国民损失尤其惨重。
这是因为,如果某个国家的邻国仍旧发行真实货币,而这个国家却想持续发行毫无价值的纸币,那是行不通的。外国人自然会拒绝接受毫无价值的纸币,最终国内就会出现买卖真实货币的黑市。
但是现在我们处于一个 “镜中世界”,在过去的 40 年中,没有任何国家发行过真实货币。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货币实验。没人知道这个实验何时结束,结果又如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实验总会有结束的一天。
第十四章 小屋價格是如何漲上去的→質借、政府政策影響房價
即便如此,銀行也不能保證收回全部貸款。因此,為了抵消這個風險,銀行要求借款人先交大量的魚作為首付。
……
为了跟上学费增长的步伐,学利美持续提高助学贷款的额度。几年以后,冲浪学校的助学贷款就成了岛民一生中极大的花销之一。
同样,在 “两棚” 的作用下,岛上的棚屋建造、棚屋销售和棚屋装修业务也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这些活动吸收了越来越多的产能,却没有换来更多的真鱼,也没有提高任何人偿还棚屋贷款的能力。
故事引申
虽然这些贷款政策看起来好像是参与各方共同受益,但实际上整个系统制造了更大的风险。
参议院推行的刺激政策向棚屋贷款和助学贷款倾斜,其他没有政府担保的贷款受到影响,扰乱了信贷市场。参议院鼓励放贷并不是因为那是使用储蓄的最佳方式,而是因为帮助人们获得棚屋和教育机会能够转化为政治资本。
因为有 “两棚” 的担保,棚屋贷款利率下调,岛民就能获得更大额的贷款。结果,就像冲浪学校的学费一样,棚屋价格也开始明显上扬。随着棚屋价格的不断上涨,在岛民看来,购买棚屋不仅仅是一笔可以承担的费用,还是一项重要的投资。人们认为购买棚屋比储蓄更划算,更能为以后的幸福生活提供保障。
参议院还宣布棚屋买卖产生的大部分利润都享受免税优惠,而且棚屋贷款的利息还可以从每年的鱼税中扣除,这就进一步刺激了棚屋行业。结果,买卖棚屋成了比创业和储蓄更有利可图的事。于是,岛上有了更多的新棚屋。与此同时岛上的储蓄和新企业不断减少。
后来棚屋价格飙升,贷款总额达到了参议院为 “两棚” 设置的上限。这时,议长考得不可避免地介入,他宣称 “两棚” 的基本状况良好,要求参议院提高贷款上限,降低首付款,降低信用标准,以确保人们买得起棚屋。他真是个常胜将军。
“两棚” 的老板都是考得的老朋友,为了答谢考得的帮助,他们为他的连任选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给考得的棚屋提供了友情贷款。
……
然而,快速飙升的棚屋价格给参议员们带来了实惠。轻而易举获得的财富让选民们感觉自己很富有,也间接证明了参议员们的英明。参议员们自然不遗余力地维持棚屋市场的繁荣增长。本・伯南柯和阿里・格林芬向所有人保证不会出现棚屋供大于求的局面,因为棚屋价格绝不会下跌。
大肆吹捧棚屋市场的人不仅仅是政治家,岛上最受尊敬的私营部门思想家吹嘘得最起劲。在衣冠楚楚的巴里・雪余子主持的脱口秀节目中,岛民们经常讨论时事。一向乐观的巴里戏称这一时期为 “金鱼经济”。卡普・盖佛等专栏作家也告诉岛民们,棚屋市场崩溃是天方夜谭,现在的银行优惠政策是前所未有的。客串嘉宾派克・希夫一向笑料百出,他警告人们棚屋市场崩溃即将来临,引起了阵阵哄堂大笑。
现实链接
现在,惨痛的事实告诉我们每个人,美现在,惨痛的事实告诉我们每个人,美国在房市泡沫膨胀和破灭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喜悦和痛苦。因此,我们必须铭记危机曾经近在咫尺,而绝大部分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金融评论家都没能预见到灾难的来临。
这就好像一场 5 级飓风已经距离迈阿密海岸仅十几公里了,气象学家却没有预报一样。主流的经济学家有多么愚蠢,似乎不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了吧?
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能看出,2006 年的房价已经高得离谱了。人们对房价的估计与对自身负担能力的估计脱节了。所有的数字都不对劲。然而,经济学家却想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理论,似乎能解释房价上涨的原因。
但是,人们没有看透这些吵吵闹闹背后的真正目的。政治家想要用虚假的繁荣维持选民高涨的自信心,企业想让消费者花钱购买他们负担不起的产品和服务,有线新闻网想通过描绘太平盛世赢得高收视率,银行、按揭贷款发放机构以及房地产经纪人想继续赚取费用和利息。这些利益集团雇用了大批的人粉饰这个最大最丑陋的骗局。而且,令人吃惊的是,人们真的接受了他们的解释。
那么,我们现在终于学会实际一些了,对吗?大错特错。即便在按揭贷款市场崩盘以后,人们仍然不明白政府政策是如何影响房价的。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斥巨资扶持下跌的房地产市场。这意味着政府和美联储对房地产市场的投入比危机发生前投入得更多。但是人们依然没有认识到,这些措施是如何支撑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并让我们以后摔得更惨的。
第十五章 快了!快了!小屋市場要崩潰了→財富假象、政府干預阻止重新分配
意想不到的結果出現了:小屋價格不是逐漸下跌,而是直線下降。小屋供大於求的現象很快演變為小屋價格的大規模下跌。
谁也说不清棚屋市场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逆转的。也许是因为备受关注的火山全景单元房项目的失败。那个项目的设施齐全、空间宽敞,还有无与伦比的海景和火山景观,但是不知为什么没人愿意购买。
曼尼是这个项目的主要担保人,项目失败后,开发商无法偿还工程贷款,曼尼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紧张的棚屋投资者看到火山全景单元房项目的损失后,开始仔细审视其他高风险的棚屋项目。一种明显的恐慌情绪蔓延开来。
很快,大小投资者都认为棚屋市场已经达到顶峰。不少人决定出售棚屋,赚取差价,等到更好的时机再投资。
但是有一个问题 —— 所有人都同时想到了这一点。大多数棚屋所有者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长期持有棚屋,所以棚屋市场刚一生变,所有人都想立即脱手。很快,岛上全是出售棚屋的人,却没人购买棚屋。这样一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棚屋价格不是逐渐下跌,而是直线下降。棚屋供大于求的现象很快演变为棚屋价格的大规模下跌。
想当年,只要拥有棚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赚钱,而如今卖棚屋却变成了赔本的买卖。由于棚屋价格不再上涨,棚屋净值不再增加,短期炒房也就无利可图。没有了利益的诱惑,过高的贷款额度成了无法承受的负担。
有些借款人本来买不起棚屋,他们希望通过棚屋的快速倒手获利或者得到 “以小换大” 的贷款,等到暂时处于低位的诱惑利率调高以后,这些人马上就无力承担棚屋贷款,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由于棚屋的价值小于贷款的金额,人们都想从巨额贷款中脱身。那些零首付购买棚屋的人尤其如此。这些借款人前期没有任何资金保证,就算不偿还贷款,让银行收回棚屋也没什么损失。
由于越来越多的借款人拖欠还贷,曼尼贷款证券化业务很快宣告破产。久负盛名的曼尼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一蹶不振。很快,“两棚” 也宣告破产。
因为消费者不再投资棚屋,其相关产业也陷入了困境。大批棚屋建筑工人、设计顾问、橱窗布置员和电器销售人员纷纷失业。
其他看似毫不相干的产业也受到了冲击。当初,“以小换大” 贷款大行其道时,美索尼亚国驴车制造商大赚了一笔。那时,棚屋不断升值,岛民不费吹灰之力就赚得盆满钵满,买的车越来越大。在棚屋市场最繁荣的那些年,很多驴车都大到需要四五头驴来拉。(问题是,大多数的驴都要靠进口。)一旦棚屋市场无利可图,这些 “草老虎” 的销量也一落千丈,驴车公司相继破产。
小岛陷入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失业工人们走投无路,都聚集到参议院门前讨说法。
故事引申
岛上最不需要的就是更多的棚屋。棚屋已经够多了,任何用于棚屋建设的资源和人力都是浪费。
同理,棚屋价格已经够高了。棚屋价格涨到如此令人咋舌的水平,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已经一去不返了。要遏制棚屋价格下跌的趋势,就像阻止一座没有任何支撑的桥倒塌一样困难。
虽然很多岛民都因为棚屋价格下跌而惴惴不安,但是如果任由棚屋价格下跌,同时停止建造新的棚屋,反而对岛上的经济有好处,至少在真正的需求出现之前是这样。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会花那么多钱购买棚屋,而是把钱花在那些经济发展中缺乏的东西上,比如新企业可能只需要一头驴拉的驴车。原本用于建设棚屋的资源,比如竹子和绳子,也可以用于新的行业。
不幸的是,政府的干预阻碍了这种资源再分配。
……
现实链接
繁荣的房市对整个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在房市繁荣的巅峰时期,房屋的融资、建设和装修成了美国经济的中流砥柱。然而,每个人都只看到了眼前的好运,却没注意到未来的损失。
不仅 “炒房者” 赚到了大量财富,普通房主们每年也通过 “以小换大” 贷款获得数千亿美元。如此一来,房产成了免税的自动提款机。人们用这些钱翻新房屋、度假、上大学以及买车和电子产品,总体生活水平比房屋升值前提高了。
但是,这些财富不过是海市蜃楼。
罗伯特・席勒在《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一书中写道,在 1900~2000 年这 100 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房价平均每年上涨 3.4%(只比平均通货膨胀率略高)。这是相当合理的。物价与人们的购买力密切相关,这也是收入和信贷可得性的作用之一。
然而,1997~2006 年,全美房价平均每年上涨 19.4%,涨幅惊人。在此期间,收入却鲜有提高。那么人们是如何支付高昂的购房款的呢?这两个时期的区别在于信贷的多寡。后期美国政府制定了许多政策,贷款利率更低,获得贷款也更容易。但是信贷不会永远扩张,最终贷款条件会变得更严格。一旦信贷收缩,房价就不可能再升高了。
所以,房市达到巅峰时,多年来不断涌入经济体中的低息贷款停止了。即便在房市开始萧条之后没有其他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有问题的),没有了那些自由现金流,经济也一定会萎缩。为了恢复经济平衡,经济衰退不是必需的,却是必要的。
但是,当经济开始收紧时,立法者和经济学家不仅不认为这一过程是多年来银根松动以及过度消费的结果,反而把它当作问题本身。换句话说,他们错把解药当作毒药。
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一直都鼓励消费者像房市崩溃之前那样消费。但是钱从哪儿来?如果失业率上升,收入和房价下降,消费者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经济学家宣称,如果人们不能消费,政府就应该采取措施帮助他们消费。但是,政府也没有多少钱。政府所有的就是税收、贷款和自己印刷的货币。税金和借款只是将私营部门的花销或投资转嫁到政府头上,印制货币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政府将新发行的货币投入流通领域,必然会抑制老百姓手中所持货币的购买力。
最近一次经济崩溃之后的几年,印制货币的做法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逆差,达到了每年一万亿美元。幸运的是,我们依然能够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大部分债务,当然主要是针对外国买家。但是,美国也采取了更简单(也更不坦诚)的方式避免损失,即通过美联储将相当一部分债务卖给了美国自己。
但是,美国不会一直拥有这样的 “好运”。最终美国政府只有两个选择:拒绝还款(告诉债主美国没钱,并商议一个解决办法),或者通货膨胀(印钱来还债)。任何一个选择的后果都很严重。拒绝还款还有可能彻底清算从头来过,是相对较好的选择。不幸的是,虽然通货膨胀在经济上影响相对较差,但是在政治上有好处。
第十六章 情形怎麼變得如此糟糕→消費降低、失業率提高、國外融資
國王有些疑惑不解:「等一下,美索尼亞國比我們富有得多。我們的購買力怎麼比得上他們呢?他們能支付更高的價錢,他們有魚邦儲備券。」
……
奥库达和他在参议院的帮手南・莎洛西正准备花费新印刷出来的成堆的钞票,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小小的细节:美索尼亚国已经完全没有存鱼了。他们所计划的所有开销都要依靠外国的资金支持。
只有外国人愿意用实实在在的货物换取他们的纸币,美索尼亚人才能维持消费大于产出的生活。因此,他们的选择很简单:
1.减少消费,用储蓄还债;
2.增大产量,卖掉多余的货物还债;
3.追加贷款,继续保持现有的消费水平。
在前两个选择中,美索尼亚人都要吃苦。要么努力工作,要么减少消费,再不然就是双管齐下。而第三种选择可以把一切痛苦转嫁给外国人。毫无疑问,参议员们勇敢地选择让外国人当替罪羊。通过这些措施,他们希望恢复消费支出,重新建立国内健康的经济环境。
故事引申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类似 “驴车换鲤鱼” 的计划具有正面影响,背阴沼泽建筑计划创造了就业岗位。这些方案确实增加了消费,创造了就业岗位,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就像参议院出资的棚屋贷款一样,这些绝不是利用岛上资源的最有效的方式。实际上,这些活动都不能扩大产能。
人们看不到的是,由于稀有的劳动力和资源都用在了参议院认为比较重要的活动上,导致很多其他的就业岗位和本来可能形成的岗位受到损失。
通过反复的实验,市场的力量会找出使用这些投资资本的最佳方式。如果企业因为误读市场而蒙受损失,投资者就会及时抽身。如果企业顺应市场要求并获得利润,就会吸引更多的资金,从而扩大产能。
这些资源如果用于制作渔网、农业用具和独木舟,效果会更好。最成功的企业应该是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生产他们最需要的东西。然而,现在很明显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自由市场,所有人都寄希望于一小撮人,希望他们能够为整个岛做决定。
但是,要记住,一国的经济不会因为人们的消费而增长,而是经济增长带动人们的消费。参议员们和顾问们都没能抓住这个真理。与此同时,大把大把的新钞票营造了经济有所好转的假象。
现实链接
一两年后,几份 GDP 报告(这些报告本身也许并不可靠)少有地出现正增长态势,一些经济学家向我们宣布,经济大萧条结束了,真正的经济复苏马上就要开始了。但此时,失业率仍然处于历史最高点,待遇优厚的制造业岗位持续减少,而薪资低、技术门槛低的服务业岗位则不断增加,许多美国人听到这样的好消息,也许会大吃一惊吧。
实际上,这次经济危机已经促使经济恢复平衡,这个过程会很痛苦,而且远未结束。2009 年,美国的存款率多年来首次升高,贸易逆差在飙升 10 年后也开始萎缩。但是,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刺激计划结束了这一进程。美国人本该回到与生产力相称的生活水平上去,但他们的计划制造了更加巨大的债务,从而延缓了这个过程。
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就在几年以后,巨大的债务终需偿还。从前那些繁荣的欧洲国家正中债务危机的子弹,到目前为止,美国还算成功地避开了这颗可怕的子弹。现在,美国暂时躲过一拳。不幸的是,美国的预算赤字年年增长,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濒临崩溃(一部分原因是婴儿潮一代退休引起的人口结构上的变化),所以这一拳迟早会来,而且会更有力。
美国政府没有显示出任何解决该问题的意愿。它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大幅削减政府支出的可能性,更别说尝试那样做了。奥巴马总统刚上任时,他要求 “逐句” 审查三万亿美元的联邦预算,以找出 “无用的开销”,但这不过是作秀而已。结果只是节省了微不足道的 170 亿美元,还不到整个预算的 0.5%。而那些提倡削减预算的人也遭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猛烈抨击。
如果美国政府不在财政上严于律己,美国的债权人(主要是中国和日本)迟早会要求美国那么做。债权人可以选择多种方式让美国就范,最有效的一招就是停止购买美国的国债。
目前,这些国家的处境与中岛帝国相似。一旦它们认识到不断向一个付不起账的顾客借钱是件浪费资源的事,就会改弦更张。那时它们就会把生产力集中到国内消费者身上,它们就能完全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了。
目前,国际上要求金融改革的呼声高涨,这些国家虽然也怨言不断,但它们还是继续借钱给美国。但是,它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现在美国一半以上的政府债务都卖给了外国政府,如果它们拒绝继续购买,谁来买美国的国债?美国国内可用的储蓄少得可怜,美国人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等到那一天到来,美国有两种选择:拒绝还款或通货膨胀。不论选哪一个,由于购买力下降和利率升高,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都会急剧下降。
第十七章 緩兵之計→量化寬鬆政策的問題
朱特尼亞群島爆發了一次更加嚴重的小屋崩潰風暴。在這個緊急關頭,一個名為 IMF(島際海上漁民組織)的跨洋機構倉促成立,並立即推出了一項計畫。
……
这一方案最终被定名为 “定量鱼券 1 号方案”,即 QF1。该方案的推出备受推崇。华孚街(Wharf Street)再现昔日繁华,大批渔船来到这里,但这次船上堆满了钞票,而不是一堆堆腐烂的鱼。这些钞票直接送到了曼尼的办公室,这些钱要用来买进拖欠的棚屋贷款,重新投资岌岌可危的企业,为学生提供低价的贷款等等。于是,棚屋价格停止下跌,逐渐稳定,最终开始上涨。人们觉得比之前富足,于是开始消费,价格也开始上涨。一切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现实链接
从 2010 年起,全世界都将目光聚焦在一出慢动作戏剧上,这出戏就是将所谓 “PIGS”(即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国家卷入泥潭的债务危机。这些国家都有着阳光充足的地中海气候、璀璨富有的历史以及待遇丰厚的社会保障体系,除此之外,它们还都是欧盟成员,其负债水平也都远远超出本国经济的发展。尽管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希腊却不幸成为这次危机的靶子。
就其经济状况的荒唐程度而言,希腊的确是个例外。据一份未经证实的财务报表(其中部分由美国投资银行高盛设计,该银行曾涉嫌金融欺诈)显示,希腊 2001 年获准进入欧元区,开始使用强劲稳健的欧元作为流通货币,作为回报,希腊要在欧元区严格的财政指导下发展经济。但是,南北欧之间政治独立与文化差异结合方式的大不同会导致严重的货币混乱局面,而那些一心想推行单一通货的设计师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尽管希腊从 2004~2006 年的房地产建设热潮中获益不少,但到了 2010 年,一个事实却越来越清晰:这个国家已经无望偿还已有的债务,更没有可能兑现自己对公民的承诺了。希腊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国家,成了短期工作、长期罢工、提早退休、连续逃税的代名词。通常来说,一个国家沦落到希腊这样的地步,会通过否认债务或货币贬值来应对危机。但作为欧元区的一员,这些做法希腊一样也不能采用。
这一事件导致的政治与经济危机,使欧洲连年稳居全球经济新闻头条。这对美国来讲倒是幸事,欧洲的诸多问题对美国而言,无异于天赐良机。希腊首都雅典大街上游行的人群不仅是经济恶化的醒目标志,还使恐惧蔓延,令整个欧洲大陆深陷泥潭。这样的剧变使许多投资基金转而越过大西洋,去寻找更安全的避风港。于是,在美国经济亟须支撑之时,大量资金及时涌入美国。讽刺的是,许多经济学家对此的评论居然是,欧洲的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负担,然而实际上,这些问题带给美国的明明是一种福祉。
尽管希腊的经济状况远不能跟美国相提并论,但并不是整个欧洲大陆都不如美国。事实上,德国(毋庸置疑是推动整个欧元区发展的经济强国)的经济状况远好于美国,但欧元区至少得共同面对债务管理失控的困境。美国政府也要做出与欧盟类似的努力才行。虽然欧洲的政治联盟仍有待完善,至少该组织还没有为欧洲开出那一剂最危险的经济药方:量化宽松。
2008 年之前,量化宽松这一概念尚未普及,只有大学经济学系的学生听说过。而过去几年间,量化宽松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影响股票、债券和房地产走势最重要的因素。尽管很多人知道美国依赖量化宽松,但很少有人真正看透其本质:向金融市场注入新的资金,以推动价格上涨。实际上,量化宽松不过是通货膨胀的一种委婉表达,它也成为美联储将政府债务货币化的隐秘手段。
但想用量化宽松政策来修复萎靡的经济,就好比企图用汽油去救火一样,汽油越多,火势就越旺。如果不知道汽油具有可燃性,你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火没扑灭是因为汽油的量不够大。要是这样的误解不消除,形势就会持续恶化,直到火势失去控制。这不正是美国当前经济状况的真实写照么?!
正如本书前文所述,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消费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货币供应量固然会鼓励人们消费,但对扩大需求却毫无裨益,而需求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第十八章 佔領華夫街→錢的錯誤分配
由失業工人、小屋購買者等年輕人組成的聯盟發起的「占領華夫街」運動,激起了公眾的想像力,成為後危機時代挫敗的象徵。
故事引申
那些愤怒的抗议者并未搞清楚,他们愤怒的矛头其实指错了对象。曼尼和他的下属不应该为这次混乱负责,该负责任的是巴斯、奥库达、格林芬和伯南柯这些人。要不是那些政客和银行家,华孚街上的融资者们早就顺理成章地被赶出华孚街了。尽管 “占领华孚街” 从未真正发展为政治运动,但政客们看到讨伐的双拳挥向了错误的方向,心中还是暗自窃喜。许多精明的参议员投票支持紧急援助,实际上是和那些抗议者站在同一战线上的。
……
同时,伯南柯开始警告人们,如果银行不发行更多的定量鱼券,价格将会面临全面下跌的危险。岛上的居民都不理解为什么价格下跌成了一个问题,如果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下降了,人们不就能买更多自己需要的东西了吗?就连商人也希望物价下跌。成本下降了,他们就可以利用省出来的钱为顾客提供优惠,也能售出更多的商品。尽管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但伯南柯和格鲁曼却使人们相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只有受过多年学校教育的人才会明白其中的奥秘。此外,两人的胡须都相当迷人,这一点在民众心中是加分项。
……
故事引申
在经济发展的迷茫期,收入的减少和对未来的恐惧会限制众多购物者的消费行为,此时,物价下跌会激起人们再次消费的欲望。所以,物价的确会对低迷的经济产生自然的刺激。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物价暴跌。尽管许多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当时暴跌的物价是那场大萧条的诱因,而非其产物,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当人们找不到工作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下降至少会带给他们一些安慰。按照那些经济学家的说法,如果人们必须同时面对上升的失业率和上涨的物价,他们的日子能好过吗?
与 20 世纪 30 年代那场大萧条不同,在 2008~2010 年的经济衰退期,生活消费品的价格从未下降。考虑到当时的经济混乱是由人们对投机极度狂热所导致的,古典经济学本来可以预测到这场混乱过后会出现通货紧缩现象。但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阻止了这种有益的经济衰退的发生。于是人们只能同时面对经济紧缩与通货膨胀两种困境。
现实链接
遗憾的是,美国人的记性总是很差。过度的借款与支出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投机泡沫,全美经济因此几乎崩溃,而似乎人们转头就忘了这些。到头来,美国人依旧欢迎那些政策以及更多同类政策,还指望它们将我们拉出经济衰退的泥淖。听上去,这样的计划当然比另一个方案(明显不讨好的选择:
消费不足、拒付债务、更高储蓄)更加容易。这就好比以毒攻毒的解酒方一样,以为宿醉之后最好的醒酒方法便是在清晨再来一口烈酒。但只要有酒鬼,这个借口就一直奏效。其实有时候,宿醉之后最好的解药就是一杯黑咖啡外加几片白吐司面包。
2008 年房市崩溃前夕,美国用巨额借款建设和售卖房屋,而实际上人们并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事实证明,这些钱用错了地方。正是由于我们把钱花在了不需要的东西上,所以才没有足够的钱来换取我们真正需要的,比如扩大工业基地。
政府并没有运用市场的影响力来调整泡沫经济,将其引向健康可行的轨道,成为能够持续有机增长的经济,而是一味使泡沫不断膨胀。经济崩溃后不久,政府借款数目超过了此前私营部门缩减的借款数目。
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于 2008 年年底和 2009 年实施。当时作为 “一次性” 计划,购买了大约两万亿美元债券,这些债券以住房抵押贷款和政府支持的机构作为担保。当时,许多 “有毒” 债券由那些最大的银行和投资基金持有,如果它们被迫在公开市场上倾售债券,其可能蒙受的损失会造成一片恐慌,市场也会随之瘫痪。若此时美联储主动介入,购买一些没人买的债券,市场就会如释重负。
然而,2010 年第一季度,美联储的购买量逐渐减少,股票市场很快抛售一空。这时,有些经济学家开始警告人们将会出现经济 “二次衰退”(double dip recession)。同年 11 月,美联储又一次启动了量化宽松政策,包括更大手笔地购买国债,这一举措使得利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但似乎没有人关心美联储的下一个更大举动 —— 购买最大规模的国债。在经典术语中,这个过程叫作 “债务货币化”。通常这一举动被视为一个国家在绝望之时所做的垂死挣扎。但在这一案例中,这个举动不过被视作促进经济复苏的正当手段而已。
在 2011 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当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逐渐停止时,市场又一次出现好转的迹象。之后,美联储推出了 “扭曲操作”(Operation Twist),即:将短期债务换作长期债务。这一计划失败后,美联储最终决定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每月投入 850 亿美元,国债与抵押债券基本各占一半。
尽管长期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为股票市场带来诸多益处,也重新造就了房屋市场的繁荣,但这一政策对真正的经济发展却作用甚微。这就是为什么在股票与价格高涨的同时,失业率却始终居高不下,实际收入则陷入停滞。
美国最终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到目前为止,美联储是国债与抵押债券最大的买家。只要这个债主停止购买,两个市场中必有一个会受到严重破坏。这种依赖情形意味着美联储一定不能破产。这也是为什么关于美联储 “退出策略” 的预测,会让步于手段更为温和的量化宽松 “递减” 策略。就连那些警告也逐渐温和起来。他们能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尽力迷惑市场,使其相信将会有真正的 “退出策略”。最终他们的蒙蔽能力也会走到尽头。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最后关头来临时,美国会有更多的债务要应对。美国的经济对于量化宽松已黔驴技穷,剩下的只有债台高筑的困境。
今天的经济学家需要看清量化宽松的真正面目:它是延长经济衰退的办法,而不是促进经济复兴的良方。经过多年的失败,他们需要试试新方法。
第十九章 無魚不起浪→惡性通膨、重回無經濟活動的魚網捕魚
魚邦儲備券持續貶值,沒人願意繼續持有它。小鼓島和狂舞島也和中島帝國一道,限制購買魚邦儲備券。賣主多,買主少,魚邦儲備券掉入了萬丈深淵。
……
不出所料,中岛帝国储备的鱼邦储备券变成了一堆废纸。很多企业倒闭,经济陷入混乱。不过,正如那位农民所预见的那样,其他的企业很快就发展起来,利用闲置的产能制造中岛帝国人真正需要的东西。
和往常一样,中岛帝国人仍旧捕鱼、制造产品并继续储蓄,由于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岛帝国没有陷入经济危机。实际上,很多产品在国内销售,国人的储蓄也都存在国内的银行里,中岛帝国的生活水平开始稳步提高。当地的工厂利用以前用于购买鱼邦储备券的储蓄购置设备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国内消费者生产的产品更多了,中岛帝国的商店里一下子摆满了商品,库存增多导致物价下跌。
正如那位农民所预料的,虽然损失了大把大把注定贬值的鱼邦储备券,但中岛帝国蓬勃发展起来。
视线回到美索尼亚国,事态的发展方向恰恰相反。目前只有很小型的捕鱼器还能用,银行的技师工作起来比以前更加拼命也更加有创意。官鱼的尺寸严重缩水,通鱼膨胀也卷土重来。
……
现实链接
纵观历史,政府总是因为入不敷出而陷入困境。一旦这个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政府就要面临艰难的选择。
选项一,政府通过提高税收增加收入。这条路从来不受人民的欢迎,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很难通过。即便在集权主义国家(那里没有烦人的选举),增加税收也会带来很多问题。高税率总是会抑制生产,降低经济活力。税率是有上限的。税率过高,人们就会停止工作。如果继续提高,就有可能发生暴乱。
削减政府支出这个选项要好得多。然而,这样做往往比提高税收更困难。利益受损的人可能会投反对票,或者到街上闹事,那些认为自己理应获得利益的人尤为明显。政客们为了赢得选举做出无数承诺,而选民们也从来不考虑纳税人能否为这些承诺埋单。
为了避免这两种在政治上不受欢迎的选择,一些政府选择拒绝还债。也就是直接告诉债权人,我们不能全额偿还。如果债权人都是外国人,这就是个很容易做出的选择。从政治上来说,与其增加税收并剥夺国人的利益,还不如失信于外国人。
对于政治领袖来说,拒不还债当然令人难堪,因为这相当于正式承认自己没有偿付能力。为了避免这一窘境,很多政客索性选择印刷钞票,引起通货膨胀,使债务贬值,等于换一种方式偿还债务。通货膨胀一向是最容易做出的选择,通常也是最后的选择。然而,选择这一方案虽然开始时好像很容易,最终却要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政府可以利用通货膨胀避免艰难的抉择,还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赖掉债务。政府可以通过加印钞票在名义上偿还债务,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本国货币的贬值。债权人收回了债务,可是却不值多少钱,如果碰上恶性通货膨胀,则会血本无归。
通货膨胀不过是把财富从以某种货币储蓄的人手中转移到以同种货币负债的人那里。如果遇到恶性通货膨胀,存款就会变得一文不值,负债却一笔勾销。(拥有固定资产的人情况会好一些,因为与以货币形式储蓄不同,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会暴涨。)这样的事情以前发生过不止一次:18 世纪 90 年代的法国,19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南部邦联,20 世纪 20 年代的德国,20 世纪 40 年代的匈牙利,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阿根廷和巴西以及现在的津巴布韦。在所有的这些例子中,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以及随后的经济灾难的原因都惊人地相似。这些国家都是通过降低货币价值偿还巨额外债,结果,本国的人民陷入了赤贫之中。
现在的美国如果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它必将成为有史以来 “获此殊荣” 的最大最发达的经济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到目前为止,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一直是美国手中的王牌。也就是说,哪怕基本面再差,世界各国还是会接受美元。然而,一旦失去储备货币地位,美元的下场就会和其他已经崩溃的货币一样。
美国必须正视这些可能性,并在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之前,及时悬崖勒马。
后 记
故事中,美索尼亚国的结局惨淡,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却未必是同样的命运。不幸的是,美国的领导人依旧推行消费计划,而且数额更加庞大,实际上正是类似的政策引起了金融危机。他们越是执迷不悟,最后的结局就越悲惨。
虽然用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应对资本主义的失败这一想法是凯恩斯首创的,但是直到艾伦・格林斯潘、乔治・布什、本・伯南克和巴拉克・奥巴马登上历史舞台以后,这一思想才开始成为体系。2002 年以前,我们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联邦赤字(现在每年都超过 1.5 万亿美元),如此大规模地实行超低利率和操控信贷市场也是前所未有的。
虽然错误如此明显,但美国还是一错再错。
早在 2002 年,也就是充斥着大量不当投资的互联网经济时期,数百亿美元的资金涌入了毫无前途的公司,那时经济本来应该进入一个长期的衰退时期。但是新当选的乔治・布什不希望糟糕的经济环境影响他连任。所以,他和顾问们选择了凯恩斯主义的解决办法,政府支出和宽松信贷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因此,2002~2003 年的这场经济危机是历史上最轻微的一次。但是,它的代价却是长期的沉重负担。这场危机结束时,美国经济失衡的现象比以前严重得多。按理说,这种情况本来不该出现。
我们期待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结果却吹起了一个更大的资产泡沫(房市泡沫),只是暂时缓解了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压力。不断上涨的房价带来了很多 “好处”,于是人们就误以为那是经济健康的明证。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强劲势头不过是海市蜃楼。
6 年后,下一次危机发生了,但美国仍然没能从这些错误中学到任何东西,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政客和经济学家们不仅误判了 2008 年经济危机的起因,还开出了错误的药方,这些错误是很危险的。
金融危机发生数月以来,大家一致认为是因为缺乏足够的监管才会酿成苦果,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政府和美联储的责任。结果,不该来的(财政支出和限制性规定)越来越多,该来的(储蓄和自由企业)越来越少。
华尔街的领袖们也很不负责任。大银行在经济繁荣的那几年赚取了惊人的利润,危机来临之后,它们本应该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银行家的这些手段都是政府授意的。美国的领导人很不理智地鼓励购房,抑制储蓄,还很不理智地鼓励借贷。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破坏了市场。
美联储、联邦住房管理局、房利美、房地美(它们一直都是伪装下的政府机构)以及其他一些机构制定了许多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房屋买卖,消除了制约信贷发放的因素。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信贷和房地产泡沫,一个在破裂之前只能继续膨胀的泡沫。
人为造成的低利率(使经济显得很健康)激活了可调利率的按揭贷款市场,还催生了诱惑利率。诱惑利率使原本高不可攀的房子显得唾手可得。艾伦・格林斯潘本人也积极鼓励购房者参与进来。政府机构和政府资助的机构仅仅根据借款人偿付诱惑利率的能力就为其担保,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没有它们的担保,大部分按揭贷款银行都不会提供贷款。
正如自由市场中的物价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是由贪欲和担忧这一组对立的情感所支配的。然而,美国政府竭尽所能试图将担忧从这一等式中抹去。
因此,在 2008 年年初市场的力量正要戳破信贷和房产泡沫的时候,美国政府插手进来继续吹大这两个泡沫。美国政府先是援助贝尔斯登和美国国际集团,并为高盛和美国银行等华尔街公司担保。然后美国财政部推出了价值 7 000 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购买私营部门不愿投入的住房抵押贷款资产。后来,美国政府又救助了为学生提供贷款的沙利美,并基本上接手了整个助学贷款市场。紧接着又救助了底特律的汽车生产商。
本应倒闭的公司又在政府的支持下站了起来,本应解放出来的资金和劳动力被困在了无效的经济活动中,无法发挥更高的经济效益。
房市泡沫破裂以后,消费者无法再那么轻松地赚钱,于是理智地停止了消费。作为应对,美国政府推出了 7 000 亿美元的巨额刺激计划。美国政府的这笔开销,是向美国民众的后代借来的。靠着这笔钱,现在的美国人不用去过量入为出的拮据生活。
美国政府拒绝顺应市场的力量,不允许严格控制过度消费,不允许错误投资变现,不允许补充已经枯竭了的储蓄,不允许为资本投资提供资金,不允许帮助工人从服务业转移到制造业。如此一来,美国政府实际上是拒绝了良药,加重了病情。在此过程中,美国把各种各样的债务都转化成了政府债务,并且吹起了另一个泡沫,这次的主角是美国国债。
一旦这一药方没能使经济成功复苏,美联储便立刻调制出药效更强的药汤,那就是量化宽松。第一套方案(QE1)推出后,紧跟着便是第二套方案(QE2)、“扭曲操作” 以及第三套方案(QE3),其中第三套方案就是当时人们所知的 “无限量化宽松” 政策。也就是说,如果一开始你没有成功,就原样重复一遍。如果还是不管用那就再做一遍,只不过动作幅度更大。如果你觉得这种描述让你感觉神经错乱,我想说,你的感觉没错!
不幸的是,这个新泡沫可能会比以往的资产泡沫都要大。这个泡沫终将破裂,必将引起物价和利率飞涨,其破坏力会比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加起来的威力还要大。
现在悬崖勒马还为时不晚。美国需要能勇敢地向选民坦白的领导人,也需要能够为经济复兴付出辛劳的选民。
多年以来,美国人一直入不敷出,现在他们必须下决心过量入为出的生活。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任由自由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他们就能重新平衡经济,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打下基础。
然而,如果他们选择寄希望于借贷、印钞机以及政府承诺的毫无痛苦的解决办法,那他们都要回到徒手捕鱼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