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之巅》(第四版)概述
前言
这本书近年来比较流行,这次终于抽时间看完了。这本书主要介绍了一些IT相关技术公司的兴衰,其中最有价值的是硅谷和斯坦福大学崛起缘由、谷歌股权分配方式和风险投资相关的内容。
书籍简介
作者:吴军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年:2019-6
页数:956
ISBN:9787115514226
作者简介
吴军,男,汉族,1967年4月出生于北京, 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前Google高级资深研究员。原腾讯副总裁。计算机科学家、畅销书作家。硅谷风险投资人。工业和信息化部顾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工学院董事、高山书院学术管理委员会成员。 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和网络搜索专家。 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 Google自动问答系统和许多创新产品的负责人。吴军博士是当前Google中日韩文搜索算法的主要设计者。著有《数学之美》《浪潮之巅》 《文明之光》《大学之路》《态度》《全球科技通史》《见识》 《硅谷之谜》 《智能时代》 《格局》 《信息传》 《吴军数学通识讲义》 《吴军阅读与写作讲义》 《具体生活》 《给孩子的科技史》《计算之魂》 《元智慧》 《软能力》 《富足》 。
2007年,他开始在谷歌黑板报(博客日志)上连载文章。他分析互联网和通信界各大企业,之后整理成《浪潮之巅》一书,一面世就成畅销书,豆瓣9.1分。吴军已经出版了10多本书,总销量超过300万套。 吴军一个特点是跨界,如果说之前出版的《浪潮之巅》《数学之美》和理工科还有点关系,那《文明之光》的跨度着实大了点。这本讲述人类文明的书,完全打破了科技与人文的界限。
内容简介
这不只是一部科技产业发展历史集……
更是在这个智能时代,一部IT人非读不可,而非IT人也应该阅读的作品。
一个企业的发展与崛起,绝非只是空有领导强人即可达成。任何的决策、同期的商业环境、各种能量的此消彼长,也在影响着企业的兴衰。《浪潮之巅》不只是一部历史书 ,除了讲述科技顶尖企业的发展规律, 对于华尔街如何左右科技公司,以及金融风暴对科技产业的冲击,也多有着墨。
《浪潮之巅 第四版》新增了6章内容,探讨硅谷不竭的创新精神究竟源自何处,进一步从工业革命的范式、生产关系的革命等角度深入全面阐述信息产业的规律性。从而,借助对信息时代公司管理特点进行的系统分析,对下一代科技产业浪潮给出判断和预测。
第四版增加了大约1/4的章节,包括:
- “八叛徒与硅谷”(关于罗伊斯、摩尔等“八叛徒”创办仙童公司,开创全世界半导体产业的事迹);
- “社交网络和Facebook”(以Facebook为核心,介绍社交网络的起源、发展和商业规律);
- “生产关系的革命”(介绍硅谷企业独到的管理特点,特别是企业中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较为合理的分配制度);
- “汽车革命”(以特斯拉和字母表(Alphabet)旗下的Waymo为核心,介绍电动汽车和无人驾驶汽车产业);
- “工业革命和颠覆式创新的范式”(介绍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历次工业革命的规律性);
- “信息时代的科学基础”(介绍信息时代企业做事方法背后的科学基础和方法论,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在管理中的应用)。
正文摘录
第四版序言
1994年,我和清华、北大的一些同事向教育部和国家提出建设中国第一个互联网主干网:教育科研网(CERNET)时,主要是出于方便大学的学者和学生进行科研、学习和国际交流,完全无法想象20多年后它不仅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并且极大地提高了全民的生活水平。可以讲,今天如果没有互联网,很难想象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如何进行。而这巨大的变化,是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完成的,因此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可以讲是人类历史上最振奋人心的一个时代。
1965年,摩尔博士提出了著名的摩尔定律,即半导体集成电路的性能每18个月翻一番。虽然最初连摩尔自己都觉得这样指数增长的时间只有10年左右,但是至今它已经维系了半个多世纪。可以讲,这半个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靠摩尔定律驱动的,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赶上了这一次技术革命的浪潮,就成为了世界的领导者。中国有幸赶上了这次浪潮,而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则因为错过这次机会而落伍了,包括欧洲、日本、俄罗斯等等。这再次说明我们国家科技兴国这项国策的重要性。
吴军的《浪潮之巅》这本书,较为全面而详尽地向读者展现了波澜壮阔的信息革命(也被称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全过程和发展脉络,可以讲是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一部传记。但是,作者在书中并没有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记录信息科技产业的发展,也没有像传记回忆录那样以企业家为中心来论述技术发展和商业的成败,而是客观地讲述了IT行业中20多个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企业从诞生、发展到饱和甚至失败的过程,尽可能系统而理性地分析了这中间成败的原因,从一些独特的角度揭示了整个信息产业发展的规律性。作者吴军虽然是几十年技术革命的亲历者,但是在讲述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没有夹杂过多的个人情感和评论,而是用了大量翔实的数据和鲜活的实例,将产业发展的规律抽丝剥茧,梳理出来。作者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是大学、工业界和投资领域相互结合的结果,这一点在《浪潮之巅》一书中有生动的描述和详尽的分析。上个世纪50年代,斯坦福大学在旧金山湾区创办了工业园,这便是硅谷的前身,后来随着晶体管之父肖克利等人的到来,那里形成了以半导体为核心的科技产业,而大学不断涌现的科研成果,风险投资的资本注入,让那里不仅产业得以繁荣,而且在随后的数次技术变革中得以引领世界科技产业的发展。从70年代到90年代,硅谷地区完成了从半导体硬件到计算机软件,再到互联网的转型;进入到新世纪之后,又在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里面的原因,我分析有这样三个:
首先是对人才的重视,以及制定了一套激励从业者,包括大学教授和学生,公司的IT人员,以及投资人的利益分配制度。在书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利用自己的发明创造,直接改变了世界,同时也让自己获得了财务自由。
其次是适度的竞争淘汰机制。随着硅谷地区的发展,当地的生活和办公成本不断提高,这促使当地不断进行产业调整和人员的筛选,使得更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和更有能力的个人留存下来。由于信息产业发展极为迅速,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无法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享受成果,而需要不断地努力创新。
最后是世界的情怀。硅谷稍具规模的企业,都是国际化程度极高的企业,它们所做的创新,都是技术驱动的创新,而那些企业家的思维方式,都是力争将产品卖到全世界。这让小小的硅谷公司能拥有全球五家市值最大的企业中的三家(苹果、谷歌和Facebook)。
上述这些经验,对我国正在倡导的双创和一带一路,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虽然这本书以介绍硅谷企业为主,但是书中也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中国信息产业的成就,从大家熟知的华为、小米等公司,到在世界上领先的在线支付和移动互联网等技术,都有详细的描述。作者还用宏观历史(Macro History)的眼光预测中国将在未来进一步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产业的进步。
对于处于信息革命时代的每一个人,作者给出了下面这样几点建议:
首先要赶上技术发展的浪潮。作者认为,一个人最大的幸运,莫过于站在了浪潮之巅,这样他可以顺势而为,在大时代里成就一番事业。回顾我自己和我身边的同事所走过的历程,正赶上互联网发展的大势,这让我们得以成为中国互联网事业的先行者,我们的科研也逐渐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其次是具有创新精神。在信息时代,不仅工业界是按照摩尔定律指定的速度快速发展的,在研究领域也是如此,一项技术会很快过时,新的技术会迅速涌现,这个时代,从来不吝惜对创新的奖励。
最后是具有合作精神。整个信息产业,有很清晰的产业链和产业规律,计算机和通信设备,从芯片制造、系统制造、软件开发和IT服务,都是环环相扣的整体,没有人能够脱离相关产业独立存在。在这个产业中,各个环节之间,通过固有的产业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浪潮之巅》一书中介绍了安迪-比尔定律,就是讲软件和服务开发商,需要通过提供新的服务,消耗掉摩尔定律带来的硬件性能的提升,从而促使整个计算机和通信产业不断进步。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一个试图脱离他人单独进步的想法都是不可行的。在今天的大学教育中,我们一直强调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这恰好和这个时代的特点不谋而合。
要将半个多世纪的信息产业发展历史写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幸的是,作者吴军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具有丰富的个人经历,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在清华读书时期注重文理兼修。吴军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算是我的学弟。此后他从事过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方面的科研工作,长期在谷歌和腾讯等知名企业任职,后来又活跃于投资领域,因此对技术、管理和金融都有深刻的认识。作为一名工科毕业生,他在写作中体现出很强的逻辑性,并且能够对现象背后的规律性有深刻的认识。
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从过去那种科技含量较低的发展模式向着以技术为驱动的发展模式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型时刻,《浪潮之巅》一书不仅是科技产业的研究人员和从业者很好的参考书,也能够让其他任何行业的读者看懂信息产业发展的规律性。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一定能够让广大的读者朋友受益。
吴建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主任
2019年6月于北京
第一版序言
最早看到吴军博士的《浪潮之巅》,是在Google黑板报上。2007年,任Google资深研究员的吴军,应邀为Google黑板报撰写文章,介绍他对互联网和IT业界兴衰变化的观察和思考。由于文章篇幅较长,被单列为“浪潮之巅”栏目分次刊出。设立该栏目的直接收获就是,Google黑板报随后人气大增,增加了大批的追随者。作为《浪潮之巅》的最早一批读者,我当时就感觉,这个系列完全应该编纂成书,如今,这个感觉变成了现实。
对于吴军,我比较熟悉,因为在语音识别领域,我们都有着共同的研究兴趣,并曾作为同事有过很多交流。吴军在清华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计算机博士学位,致力于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研究。我在2005年加入Google时,吴军已经在那里工作多年。他在Google期间参与主持了许多研发项目,并在国内外发表过数十篇论文、获得和申请了近十项美国和国际专利。
我认识很多顶尖的工程师,但具备强大叙事能力的优秀工程师,我认识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而吴军是其中之一。从AT&T、微软、Google、思科等引领整个时代浪潮的公司历史叙述,到硅谷之所以成为科技中心所依靠的天时、地利、人和因素,再到科技公司发展壮大过程中风险投资、银行、产业规律各自扮演的角色,以及新时代背景下金融危机和云计算(Cloud Computing)为科技产业带来的冲击和革命……虽然每个人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通过这本书中看似波澜不惊的行文,你会读出一个从事互联网行业十多年的“老行家”个人独到的见解,以及一个身处“浪潮”中的“弄潮儿”的切身体会。
作为“兼才”,《浪潮之巅》恰恰因此具备了两方面的优势。首先,作为一位曾每天与程序、算法、科研打交道的Google最优秀的研究员,势必能更客观地描述那些科技公司的兴衰得失,不会人云亦云,更不至于离题万里;第二,作为一位拥有写作天赋的工程师,吴军能够确保文章的有趣与可读,不会容忍自己的作品成为一本呆板的教科书式读物。
《浪潮之巅》又不仅是一部提供“快乐阅读”的大公司商业史,它融汇了作者多年来的所见所闻,更包含了大量的独立思考与独特见解。这份心血,不仅是他个人的天赋使然,也是他始终在研究领域孜孜不倦的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吴军的文章,没有将目光局限在大洋彼岸,内容上也不仅是停留在对若干巨头企业的探查。作者试图从整个产业链上向读者揭示科技公司的运作规律,并通过大量的调研与观察,客观分析中国本土企业在这次科技浪潮中的地位与影响。实际上,作者吴军本人也已离开了Google,目前正在一家中国著名互联网公司担任其核心业务的领军人物。
《浪潮之巅》不是一本历史书,因为书中着力描述的,很多尚在普及或将要发生,比如微博与云计算,又比如对下一代互联网科技产业浪潮的判断和预测。从文字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科技、对创新、对互联网都充满“虔诚”信仰,并为之激情四射。
我想,对所有身处并热爱高科技行业的人来说,对所有渴望创新、欣赏创新的中国创业者来说,《浪潮之巅》都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作品,足以做到“开卷有益”!
2011年4月于北京
前言 有幸见证历史
近一百多年来,总有一些公司很幸运地、有意无意地站在技术革命的浪尖之上。一旦处在了那个位置,即使不做任何事,也可以随着波浪顺顺当当地向前漂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在这十几年到几十年间,它们代表着科技的浪潮,直到下一波浪潮的来临。
从一百多年前算起,AT&T公司、IBM公司、苹果公司、英特尔公司、微软公司、思科公司、雅虎公司和Google公司,也许还有接下来的特斯拉公司,都先后被幸运地推到了浪尖。虽然,它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中间有些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但是它们都极度辉煌过。它们都曾经是全球性的帝国,统治过自己所在的产业。
这些公司里面的人不论职务高低,在外人看来都是时代的幸运儿。因为,虽然对于一个公司来讲,赶上一次浪潮不能保证它长盛不衰;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讲,一生赶上这样的一次浪潮就足够了。对于一个弄潮的年轻人来讲,最幸运的,莫过于赶上一波大潮。
加拿大作家格拉德威尔(Gradwell)在《异类》(Outliers)一书中介绍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75人中,有1/5出生在1830—1840年的美国,其中包括大家熟知的钢铁大王卡内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这一不符合统计规律的现象的背后有着必然性,他们都在自己年富力强(30—40岁)时,赶上了美国内战后的工业革命浪潮。这是人类历史上产生实业巨子的高峰年代。而第二个高峰年代就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20年间,出现了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太阳公司的创始人安迪·贝托谢姆和比尔·乔伊、戴尔公司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Google的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等,因为他们在自己年富力强时幸运地赶上了信息革命的大潮。
出生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人,都有幸亲历了全部或部分信息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历史上科技进步最快,财富增长最多的年代。而尚未投入到技术革命大潮中的年轻人也不必担心错过了一个历史机遇,因为新的一场更深刻的智能革命已经拉开了序幕,那将是人类历史上又一个伟大的时刻。2016年年初,Google的AlphaGo围棋软件在五番棋的比赛中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九段,这标志着机器智能的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此之前,计算机已经开始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替代人的工作,而这个趋势还会随着大数据的应用和机器学习的进步不断加速。未来几十年,整个科技产业依然精彩。很多人希望我预测未来,但这其实是做不到的,而且我一直在强调适应比预测更重要。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了解过去和现在,熟悉科技产业的发展规律,培养正确的做事方法,适应未来的变化和挑战。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将这些年来看到的和听到的人和事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帮助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对当今世界科技产业的发展有系统的了解。我会谈一谈我对每次浪潮的看法,对上述每个公司的看法,以及对其中关键人物的认识。在极度商业化的今天,科技的进步和商机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也要提到间接影响到科技浪潮的风险投资公司,诸如凯鹏华盈和红杉资本,以及百年来为科技公司捧场的投资银行,例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等。另外,科技产业的兴衰成败,和全球大的经济政治环境也是分不开的,因此,从第三版开始,我特意分析了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特别是中、美两国的情况,大家可以体会为什么我一直对中国的未来有信心。
本书最初应崔瑾女士的约稿,以博客的形式在Google黑板报上连载。后来JUSTPUB出版团队负责人周筠女士和我约稿,并且在2011年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第一版纸本书。由于信息科技产业的世界格局变化很快,因此,在2013年和2016年我们对本书做了适当的修订,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第二版和第三版。三版加起来已经销售了40多万套。在此之后,我又将自己在几所大学商学院里讲述硅谷的历史和管理特点,结合我对产业规律的认识,写成了一本新书《硅谷之谜》,作为《浪潮之巅》的续集。在随后的两年半时间里,整个科技产业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促使我对《浪潮之巅》进行更新。在这一版(第四版)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将第三版的《浪潮之巅》和后续的《硅谷之谜》一书合二为一。这样在书中既讲述了信息产业历史和各大公司发展和兴衰的历程,又兼顾了对IT产业规律的论述,以及对信息时代公司管理特点的系统分析。
第四版增加了大约1/4的章节,包括:
- “八叛徒与硅谷”(关于罗伊斯、摩尔等“八叛徒”创办仙童公司,开创全世界半导体产业的事迹);
- “社交网络和Facebook”(以Facebook为核心,介绍社交网络的起源、发展和商业规律);
- “生产关系的革命”(介绍硅谷企业独到的管理特点,特别是企业中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较为合理的分配制度);
- “汽车革命”(以特斯拉和字母表(Alphabet)旗下的Waymo为核心,介绍电动汽车和无人驾驶汽车产业);
- “工业革命和颠覆式创新的范式”(介绍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历次工业革命的规律性);
- “信息时代的科学基础”(介绍信息时代企业做事方法背后的科学基础和方法论,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在管理中的应用)。
此外,原先的章节有一半是重写的,其他也进行了更新。这一版之所以进行如此之大的变动,不仅在于在过去的三年里科技产业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也因为我这几年对技术和信息产业的理解有了一些更新。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给几所大学以及社会上的商学院讲授了大约200学时的课程,对商业现象背后的本质,以及现代管理背后的理论做了研究,我将这些内容加进了这一版的书中。
写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很多人的帮助和鼓励。从我开始写黑板报算起,李开复博士、崔瑾女士、周筠女士、Google和腾讯的数百名年轻人,以及成千上万的博客读者,就一直扮演着“陪跑人”的角色,鼓励我完成这个系列博客。而将博客变成书,又有非常多的细节工作要做。Google的工程师吴根清和单久龙先生,快手的创始人宿华先生(Google前工程师)帮助我校对了第一版的部分章节。JUSTPUB的创始人周筠女士、编辑胡文佳女士和特约编辑李琳骁先生在每一版的出版过程中,都细心核对、校验了书中的资料数据,反复润色了文字,不厌其烦地调整了版式,尽最大可能把这本书做得尽善尽美。著名书法家、瀚海智业投资管理集团的董事长王汉光先生一直热心地在IT行业宣传推广我的作品,并且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屹珂设计的陈航峰先生为本书完成了封面设计工作。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浪潮之巅》的出版和传播过程中,中国工信出版集团前董事长季仲华先生,人民邮电出版社社长顾翀先生,人民邮电出版社的分社社长俞彬先生、刘涛先生,同事陈冀康、蔡思雨、孙英、贾璐帆等,电子工业出版社前社长敖然先生,编辑李影女士,先后付出了很多心血,非常感谢他们扎实积极的工作。此外,很多大学的商学院将本书作为MBA课程的教科书或者参考书,有不少高校的计算机学院和软件学院把《浪潮之巅》作为大一新生学习《计算机导论》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为它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其中要特别感谢上海交通大学的王延峰教授,以及新东方创始人兼理事长的俞敏洪先生。微软公司的邹欣老师、清华大学的史元春教授,无码科技创始人冯大辉、百姓网创始人王建硕等业界朋友,一直在不同场合向IT界的年轻人积极推荐本书,衷心感谢他们的支持。国内各大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福布斯》杂志和澎湃新闻网等,为我提供了传播的平台,热情介绍书中的内容,在此我要对这些媒体和相应的工作人员表示真诚的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在本书的创作、改版和传播过程中,给予我的鼓励和帮助,没有她们的支持,我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完成做研究、讲课和写作的任务。特别要感谢我的夫人张彦女士多次通读书稿,更正了很多细节错误。
由于当今信息产业发展迅速,新的技术和商业发展在不断更新我们的认知,加上本人学识有限,书中难免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疏漏之处,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帮助我将这本书不断完善。
2019年4月于硅谷
第1章 帝国的余晖 AT&T公司
1 百年帝国
2 几度繁荣
3 利令智昏
4 外来冲击
结束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通信始于亚历山大·贝尔发明的电话和他创立的AT&T公司。在AT&T公司盛年时期,贝尔实验室的杰出科学家香农博士第一次量化地描述了信息,并把人类带人用信息论指导的时代。数字通信随之诞生,并目让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受益。但是,AT&T这个靠信息起家的帝国却倒在了从20世纪末开始的全球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许多人为此遗憾,他们假设“如果AT&T不拆分”“如果AT&T及时进人互联网领域”“如果AT&T不犯那么多致命的错误”,等等,结果是否会好些。我的观点是,如果让AT&T重来一次,它犯的那些错误可能一样都不会少,因为它到年纪了。没有人能活两百岁,也没有公司能辉煌两百年,这就是规律,很难超越。今天,我们依然传扬着贝尔实验室昔日的辉煌,就如同我们传颂着古老中国强汉盛唐时期的文治武功、西方罗马帝国的传奇一样。毕竟,AT&T是在历史上为人类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公司。
AT&T大事记
1875 贝尔和沃森发明电话。
1877 美国贝尔电话公司成立。
1880 贝尔长途电话业务开通。
1892 长途电话业务进入美国中部芝加哥地区。
1913 和美国政府达成第一次反垄断协议。
1915 电话业务进入美国西部旧金山地区。
1925 贝尔实验室成立。
1972 UNIX操作系统和C语言诞生于贝尔实验室。
1982 美国司法部打赢了长达8年的针对贝尔电话公司的反垄断官司。
1984 美国贝尔电话公司被拆成AT&T和8家地区性贝尔公司。
1996 AT&T主动地一分为三,包括新AT&T、朗讯和NCR。
2000 朗讯的移动部门Avaya单独上市。
2001 AT&T再次主动拆分,变为独立的AT&T(含企业服务和个人业务)、AT&T移动和AT&T宽带等公司。
2004 AT&T被道琼斯指数除名,从地区性贝尔公司发展起来的SBC替代了它在该指数中的位置。
2005 AT&T被SBC并购,成为新AT&T。此前,从AT&T分出的几家独立公司均被竞争对手或业界同行收购。
2006 朗讯被法国的阿尔卡特并购,原来的美国贝尔电话公司(AT&T)从此消亡。
第2章 蓝色巨人 IBM公司
1 赶上机械革命的最后一次浪潮
2 领导电子技术革命的浪潮
3 错过全球信息化的大潮
4 他也是做(芯)片的
5 保守的创新者
6 内部的优胜劣汰
7 回归服务业
结束语
IBM百年来在历次技术革命中得以生存和发展,自有其生存之道。它在技术上不断开拓和发展,以领导和跟随技术潮流;在经营上,死死守住自己核心的政府、军队、企事业部门的市场,对进人新的市场非常谨慎。迄今为止,它成功地完成了两次重大的转型,从机械制造到计算机制造,再从计算机制造到服务。它错过了以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浪潮,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基因决定的,但是它平稳地渡过了历次经济危机。今天,它仍然是世界上员工人数最多、营业额和利润最高的技术公司之一。2011年,IBM的市值终于在20多年后,超过了老对手微软公司,可见保守和稳妥的好处。今天,IBM依然在随着科技发展的浪潮顺顺当当地发展着,易然不像过去那么光鲜,但是在智能化大潮到来时,它依然没有落伍。
IBM大事记
1924 老沃森控股原制表机公司,改名IBM。
1925 进人日本市场,此前制表机公司已经开始逐渐进人欧洲市场。
1933 IBM工程实验室成立。
1936 在罗斯福新政时,IBM获得美国政府大订单。
1940 20世纪40年代进入亚洲市场。
1943 IBM研制出真空管放大器。
1945 沃森实验室成立。
1952 小沃森成为IBM总裁,开始了快速发展的20年计算机时代。
1953 研制出倬用磁鼓的计算器。
1962 IBM开始最早期的语音识别研究,是识别10个数字和加、减、乘、除等六个单词。
1964 IBM S/360大型计算机问世。开始从事语音识别的研究。
1969 司法部对IBM展开反垄断调查。
1971 小沃森退休。
1973 江崎玲于奈(Leo Esaki)博士因在电子隧道效应上的研究为IBM获得第一个诺贝尔奖。
1981 IBM PC诞生。
1993 郭士纳执掌IBM,开创IBM的黄金十年。
1997 计算机深蓝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
2005 IBM将PC业务卖给联想,从此退出PC市场。
2006 IBM和Google、亚马逊一道,成为最早提出今天云计算概念的公司。
2014 IBM将x86服务器业务卖给联想,表明它进军云计算市场的决心。
2016 IBM宣布它的Watson医疗服务机器人在癌症诊断方面达到了和人类医生99%的一致性。
第3章 “八叛徒”与硅谷
1 怪杰肖克利
2 “八叛徒”
3 集成电路
4 硅谷的出现
硅谷为什么出现在旧金山湾区,这里面有很多巧合的因素,而那些巧合的背后,又有着必然的联系。在诸多因素中,有三个因素具有决定性。
1951年,斯坦福大学的特曼教授为了帮助大学解决财政问题,提议大学拿出2.7平方公里(600多英亩)土地创立了斯坦福工业园(今天叫做斯坦福研究园),吸引来很多高科技公司。关于这个故事的细节和它的影响力,我们在后面第17章介绍斯坦福大学时会详细介绍。
1952年,IBM在旧金山南部100公里的圣荷西市建立了西海岸研究实验室,即今天的IBM爱曼登研究中心(Almanden Research Center,见本书图2.4),这让远离东部科技中心的北加州地区有机会站在了科技产业前沿。在此之前,加州地区的科技发展要大大落后于美国东北部从北大西洋到新英格兰的各州。以计算机的发展为例,当1946年世界第一台计算机埃尼亚克(ENIAC)在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之后,IBM就把它未来的产品重点从传统的制表机等办公设备转到了计算机产业,并且通过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合作,使得计算机的技术快速取得进步。当时的加州计算机技术发展十分落后,虽然伯克利在1951年也研制出一台电子计算机CALDIC,但是这台计算机在整个计算机发展史上影响甚微,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整个加州与计算机相关的产业也几乎为零,更不用说拥有多少计算机领域的人才了。IBM的到来,则给北加州带来了计算机行业的正规军,让那里得以迅速赶上了随后而至的技术革命浪潮。
有能够不断生出“金蛋”的仙童公司,在当地孕育出完整的半导体产业,当然这同时也伴随着仙童公司最终的解体。在这个过程中,拉斯特等创始人的离开倬得半导体技术的扩散和仙童公司的解体变得无法逆转。
在诺伊斯等人发明了集成电路之后的头两年里,集成电路的制造成本比较高,以至于放弃掉原有的晶体管业务单独发展集成电路是无法挣钱的。如此一来,仙童的老板菲尔柴尔德和公司内的高管在公司的业务上就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以“八叛徒”之一的拉斯特为代表的一部分经理认为应该优先发展集成电路,并且在做新的一年的预算时,提出应该优先建一个制造集成电路的工厂。而菲尔柴尔德则认为应该优先制造当时技术成熟市场需求更大的晶体管,并且首先将钱用于扩大晶体管的产能。当然,菲尔柴尔德并不管理公司,而是通过不断向公司指派职业管理者控制着仙童公司。任何公司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样的发展路线的争执总是少不了,甚至很难说激进的和保守的路线哪一个更好,因为每一种情况都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但是,在仙童公司,这件事说明没有了股权的经理们其实很难拥有决策权。拉斯特希望当时的总经理诺伊斯能站到他这一边,而作为集成电路的发明人诺伊斯当然支持发展集成电路,但是他的性格略有一些优柔寡断,而且是一个两头都不愿得罪别人的好人,因此他希望拉斯特能再等一等,让他和管理层其他成员商量一下。拉斯特可不愿意等,因为失去集成电路的机遇太可惜,他直接给投资人洛克打了电话。
洛克和“八叛徒”中的每一个人都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并目总是乐于帮助他们每一个人开创事业。当他得知拉斯特的宏大计划在仙童施展不了时,便为拉斯特找了他所投资的Teledyne公司的老板,由Teledyne出资创办一家全资半导体公司,为军方提供半导体元件。这一年年底,拉斯特拉上“八叛徒”中的另一位霍尔尼,决定“叛逃”到Teledyne,创办他们的新公司。最后到真的离开仙童公司的时候,他们俩还拉上了“八叛徒”中的罗伯茨。他们三人在洛克和Teledyne公司的支持下创办了Amelco半导体公司。Amelco和它的母公司Teledyne很快成为了美国军方(包括航天工业)重要的半导体器件提供商,并且直接和仙童公司竞争。
就在拉斯特等人离开的第二年(1962年初),仙童的另一名基层技术主管戴维·艾力森(David Allison)带着几名工程师得到华尔街的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的投资,创立了另一家和仙童面对面竞争的Signetics公司。三年后,Signetics的集成电路产品让包括仙童在内的所有半导体公司都相形见拙。又过了几个月,诺伊斯亲自招进来的奈尔和摩尔的助手豪斯(Spittle House)离开仙童,创办了Molectro公司,并目当年就被仙童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国家半导体公司收购了。从此,原本在美国东部的国家半导体公司也就进入了硅谷,并目能够研制自己的集成电路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克莱纳也离开了仙童,去做天使投资了。十年后他创办了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基金公司凯鹏华盈。克莱纳是第四位离开仙童的创始人,这距离仙童公司的成立仅仅过去了3年的时间。
不仅技术人员在不断离职,其他部门的一些主管,包括负责销售的副总经理唐·瓦伦丁等人也纷纷离开仙童公司。瓦伦丁在国家半导体公司度过了短暂的几年职业生涯后,创办了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红杉资本。
仙童对创始人和高管的出走、员工的跳槽开始变得习以为常,听之任之了。这创造了硅谷的另一种文化——从现有的著名公司中离职,直接创业。
不过,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仙童公司依然是全世界半导体行业的领导者,诺伊斯和摩尔还在利用他们个人的魅力和宽松的管理方式不断吸引新的人才加入。但是最终,管理层和技术人员与菲尔柴尔德以及他所指派的职业经理人,在管理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到了1968年,诺伊斯也觉得如果自己在仙童公司再待下去,将会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当时,诺伊斯和摩尔希望发展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即将过去很多小规模的集成电路集成到一个芯片中,这样对顾客有很大的好处,而作为公司老板的菲尔柴尔德则希望多卖芯片。如果将十个芯片减少为一个芯片,仙童公司短期内的收入必然会减少。最终,诺伊斯和摩尔发现在这家他们创办的公司中,两人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就干脆离开仙童,创办了一家新的半导体公司,这就是后来改变世界的英特尔公司。关于这一段历史,我们会在后面第6章介绍英特尔公司时详述。
就在诺伊斯和摩尔离开仙童之后,“八叛徒”中的另外两个人格里尼克和布兰克也陆续离开了,至此,仙童公司的传奇画上了句号。易然它在后来还独立存在了很多年,但是它对世界半导体产业的影响力就此结束了,一个时代终结了。
仙童公司对世界的贡献不仅在于发明了集成电路,更在于将半导体促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行业。根据阿伦·拉奥在《硅谷百年史》中的介绍,上个世纪60年代末全世界的IT公司巨头们在开会时发现,九成以上的人都曾在仙童公司工作过。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仙童公司是全世界半导体公司之母。如果没有仙童公司,我们今天或许依然能广泛倬用半导体集成电路,但是绝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普及。
仙童公司成就半导体产业的做法听起来匪夷所思,它并非靠自身发明了多少产品,创造了多大的市场,而是靠不断地分离出子公司和孙公司,让半导体公司在旧金山湾区遍地开花。截止到2017年,从仙童公司直接和间接分离出去的大中型公司多达近百家,它们包括英特尔、AMD等知名公司。另外,今天苹果公司第三位创始人、公司第一任董事长马库拉也来自于仙童公司。这些公司的市值加起来接近30000亿美元。可以说,旧金山湾区之所以能成为硅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仙童公司。
和仙童公司同时期发明集成电路的德州仪器公司,由于地处相对保守的得克萨斯州,因此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员工离职创业的现象,这倬得该公司不仅一度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和最有竞争力的仪器设备公司,而目直到今天,它依然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半导体公司之一。德州仪器公司和仙童显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公司发展方向,前者利用一种核心技术将公司做大做强,成就百年老店;后者通过不断的叛逆行为,将技术迅速扩展到整个地区乃至全世界,创造出一个地区的繁荣。我们在前面讲过的AT&T和IBM公司,后面会讲到的微软公司都具有前者的特点一一它们的崛起通常也能带来一个地区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有很大的依赖性和危险性,因为这些巨无霸公司一方面抑制了新公司,特别是竞争对手的出现,另一方面也倬得当地在产业转型时迅速落伍。而仙童公司以及后来的思科公司、雅虎公司、PayPal公司则属于后者,它们不断派生出新的公司,甚至扶持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这些公司都有希望成为垄断企业,但是它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通过技术的传播,创造了一个地区持续的繁荣。正是靠叛逆和对叛逆的宽容,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旧金山湾区变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硅谷。
1971年,旧金山地区的新闻记者唐·霍夫勒(Don Hoefler)在一份很小的报纸上首次倬用了“硅谷”一词(图3.5),从此,旧金山湾区就有了一个具有现代气息的新名称。
硅谷对于世界工业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半导体企业集中的地区,更在于发展出一种新的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关于硅谷的奇迹以及它长盛不衰的原因,我们会在第13章“硅谷奇迹探秘”中作仔细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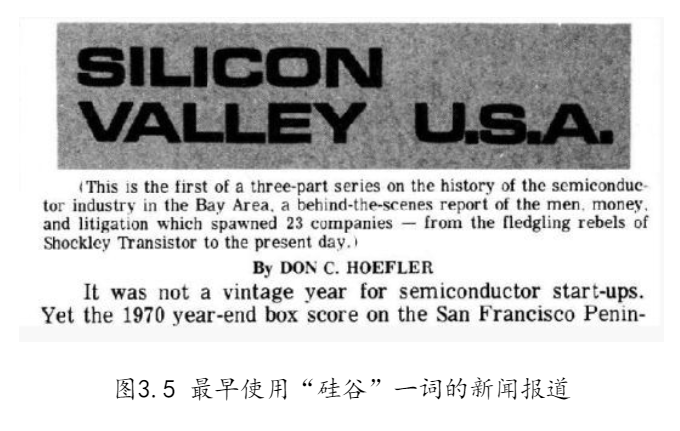
图3.5 最早使用“硅谷”一词的新闻报道
结束语
硅谷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肖克利和他带来的“八叛徒”。我们常说做成一件事情需要人和,但是硅谷的兴起却说明一个地区的繁荣需要有叛逆精神。“八叛徒”离开肖克利这件事可以解释为是一个个案,是老板糟糕的管理方式所导致的,但接下来仙童公司的不断分崩离析,就诠释了信息时代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一家公司很难也没有必要像工业时代那样通过拥有生产资料来把大家组织到一起了,另立门户的成本非常低。要想把员工们组织起来长期发展,必须拥有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而硅谷经过探索,找到了这种生产关系。
通常一种革命性新技术的出现,会导致一家巨无霸企业的诞生,这对一个地区来讲既是好事也是潜在的风险,因为一棵参天大树可以带来荫凉,但同时也会让它阴影之下的植物无法生长。然而,“八叛徒”的行为使得新技术出现时没有出现这样的参天大树型企业,相反却催生出一片森林,把旧金山湾区这个蛮荒之地变成了繁荣的硅谷。
(本书将在第22章“生产关系的革命”中,介绍诺伊斯等人和菲尔柴尔德等人之间矛盾的本质。)
第4章 科技产业的时尚品牌 苹果公司
1 传奇小子
2 迷失方向
3 再创辉煌
4 大难不死
5 i十年
6 乔布斯和盛田昭夫
2011年10月5日,56岁的传奇人物乔布斯走完了他极富戏剧性的人生历程。他一生战胜了无数的对手,但是和所有人一样,他最终输给了死神。乔布斯去世的消息传出,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他的逝世表示了哀悼。伴随着他的传记《史蒂夫·乔布斯传》的出版以及苹果新一款手机iPhone 4S的问世,已经离世的乔布斯再次成为新闻人物,并且上了《时代周刊》《经济学人》等有影响力的杂志封面。两个星期后,乔布斯渐渐从美国人的话题中淡去、消失,但依然是中国人的热点话题。不过,对他已经可以盖棺定论了。虽然在中国乔布斯已经被神化,但是在个体自我意识很强的美国,人们对他的评价远没有中国人高。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当年明月在他的畅销历史读物《明朝那些事儿》中将皇帝分为“好皇帝、好人”“好皇帝、坏人”“坏皇帝、好人”和“坏皇帝、坏人”四种。乔布斯易然不是皇帝,考虑到他在很多人心中的地位比皇帝高多了,我们也不妨这么划分。他是一个能干的传奇人物,但算不上好人。
作为凡人的乔布斯实在说不上是好人。在他看来,朋友的友谊还抵不上几千美元。乔布斯一生没有什么挚友,憨厚老实的苹果共同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知道乔布斯对他的欺骗以后,伤心落泪。乔布斯一生挣了80亿美元的巨额财富,他生前除了为养父养母付清了几十万美元的房贷,没有给过什么人钱,除了为治疗他的疾病给癌症研究进行过捐助,没有任何其他捐助。这在美国的富豪中是无法想象的。在美国,真正的富豪不是看挣多少钱,更不是看花多少钱,而是看捐多少钱。历史上的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以及现在的巴菲特、盖茨和布隆伯格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从这个角度讲,乔布斯不是典型美国意义上的有钱人。另外,乔布斯早年拒绝承认他的女儿,虽然是非婚生的,这在强调家庭价值的美国是无法让大众接受的。加上他暴君式的性格,有时粗暴的言语,包括在面试候选人时问及别人的性事这样不体面的做法,都不讨人喜欢。因此,美国人对他的为人评价并不高。
但是,作为发明家和魔术师的乔布斯,却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对个人电脑工业的贡献、对产品品质的追求以及在艺术和技术结合方面令他人无法望其项背的境界,在他的传记和各种报道中已经讲得太多了,不再赘述。这里我们通过一个真实采访的内容,看看真实的魔术师乔布斯。
2011年10月初,乔布斯过世后两天,我在美国接到一个意料之外的电话。电话是腾讯网的总编陈菊红女士打来的,她讲自己刚好在美国,想采访一下苹果内部熟知乔布斯的人。那些尚在苹果公司的人给出的都是千篇一律的官方说辞,毫无新闻价值,因此我介绍她去采访了乔布斯的老朋友、上个世纪80年代苹果的副总裁迈克尔·穆勒(Michael Muller,1938一2018)先生。陈菊红回来后说,收获颇丰。
穆勒和乔布斯是20世纪70年代认识的,当时他们都还年轻,会一起骑着意大利产的自行车,穿行在伍德赛德(Woodside,加州的一个小镇)的山路上。当时,穆勒的公司TKC(The Keyboard Company)为苹果供应键盘。1976年,苹果的生意很好,他们向穆勒提出这年需要大量的键盘。为了备足这么多键盘的配件,穆勒的公司资金不够。这时乔布斯动员穆勒把公司卖给苹果,当然条件是以后不能再帮别人生产东西了。穆勒考虑了一下,还是同意了。从此,他就成为苹果的副总裁,一干就是7年,直到乔布斯离开苹果。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苹果公司已经很大了,可是乔布斯等人工作起来还是没日没夜的。当时的键盘在技术上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敲快了,连字母切换都很有难度,一不小心按一次A就跳出来两三个,这不光需要技术,还涉及成本。但乔布斯基本不去讨论可能性,只是很清楚地表达自己非常具体的愿望。而目乔布斯的主意变得很快,半小时前,他同意说这些机器上的配件都标准化了吧,当团队快速行动已经开始讨论执行的时候,半小时不到,他却突然出现在门口,对大家说,我有了新点子,咱们得做点不一样的。据穆勒回忆,“当键盘越变越好用的时候,乔布斯想要的却是另一个东西:只有屏幕,没有键盘的电脑”。这些想法导致了后来的麦金托什和iPad。可见乔布斯这些改变世界的发明绝非一时的灵感所致,而是数十年的深思熟虑和经验的积累。
当第一次看到CD的时候,乔布斯拿起一张,里面也就只存5首歌。他把CD插进硕大的播放器,回来后穿过董事会的桌子,对大家说,看,这个东西会成为未来!那个年代,他已经在琢磨里面的内容(音乐)意味着什么。他的远见,经常穿透时间,直接看到他想象中的结果。从现在看,也是乔布斯,通过他的产品iPod,一手把CD送往终点。从见到CD到iPod问世,又是20年的时间,看似是灵机一动,岂不知已经孕育了两个十年。大多数产品经理之所以做不出改变世界的产品,是因为他们只看见了成功者最后的临门一脚,而忽视了别人的长期思考。
一天乔布斯跟穆勒说,走,我听到一个有趣的东西,咱们去看看。他们来到一个动画实险室,离金门大桥不远,屋子很小,里面只有三个人。乔布斯和穆勒坐在三个显示器前,看到电脑上出现海面,然后海风吹过,浪花飞溅在屏幕上栩栩如生。他们俩都很兴奋。三个做动画的在一个小实验室里,很开心地给他们演示。乔布斯看到的可不只是什么动画。1986年他买下了实验室,也就成了后来的皮克斯(Pixar),也就有了《玩具总动员》。在乔布斯做的大多数“改变世界”的事情中,原创并非他自己,但是拿着魔术棒“点石成金”的人却是他。如果我们承认乔布斯的创作力,那么创新就远不止是原创,而更多的是发现价值,点石成金。
1981年,穆勒住在纽波特比奇(Newport Beach,位于南加州)。乔布斯想说服穆勒搬到洛斯加托斯(Los Gatos,加州湾区)附近去住。穆勒跟着乔布斯去到他安在洛斯加托斯的家,一座很大的西班牙式建筑。院子里停着一辆黑色的宝马自行车(他极少碰那辆车,只是喜欢它的设计),偌大的房间里,只有餐桌和旁边的两把椅子,加上客厅里的一架白色的Bösendorfer三角钢琴。房间里面空空荡荡,因为对产品品质格外偏执的乔布斯几乎看不上任何家具。而另一方面,他对真正堪称精品的产品则有着非同寻常的喜爱,比如穆勒提到的宝马自行车、Bösendorfer钢琴以及他自己经常挂在嘴边的保时捷汽车。后来,乔布斯先后搬到了伍德赛德的穆勒家附近,以及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同样是很少的家具,一架钢琴。这就是他生活的样子,简单,少量,专注。
穆勒说,乔布斯总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就专注去完成。从苹果一开始就是这样。1996年,乔布斯回到苹果,他走进会议室,看到白板上14条产品线,拿着笔画了好多个叉叉,转过身,只剩下四个。穆勒说,乔布斯的这些叉叉,从死亡线上救回了苹果。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作为IT行业领袖的乔布斯,那应该就是魔术师,他有化平凡(如果不是腐朽)为神奇的本领。但在这个本领的背后,是几十年的专注和努力,以及对品质的追求。
有人将他和爱迪生相提并论,这确实有些太夸张了,毕竟爱迪生开创了整个电的时代,影响至今。而随着乔布斯的离世,他的影响力已开始式微。我想,准确定位乔布斯最好的参照系应该是被称为索尼先生的盛田昭夫了。作为盛田昭夫曾经的崇拜者,乔布斯如果知道别人把他比作盛田昭夫(图4.7),应该很满意了。
随着经济和国力的发展,中国似乎已经不满足于借鉴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而是直接一切向大洋彼岸的美国看齐,在学习管理经验上更是如此。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日本是更适合中国的老师。而在带领日本全面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出了一批世界级、面向国际的经营管理和产品设计大师,索尼公司的共同创始人盛田昭夫是其中最杰出的一员。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全世界范围来看,盛田昭夫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乔布斯。或者说乔布斯是21世纪初期的盛田昭夫。遗憾的是,21世纪的中国对盛田昭夫的了解远不如对乔布斯的认识。
在苹果进入i十年以前,索尼公司在电子产品上的地位和今天的苹果相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盛田昭夫的功劳。作为优秀的产品设计者,盛田昭夫直接领导了Walkman随声听的设计和开发,这款听音乐的产品当时在世界上的轰动效应完全抵得上后来的iPod。而在此不久前,盛田昭夫利用他的谈判技巧,迫使飞利浦公司开放了卡式录音带的格式标准,并在与美国RCA的标准竞争中获胜,成为我们使用了40年的盒式磁带的世界标准。同时,盛田昭夫还引进了另一名音乐产业的奇才大贺典雄,后者设计了我们今天的音乐CD标准。就如同乔布斯开创了个人电脑工业一样,盛田昭夫开创了数字化的音乐市场。作为领导者的盛田昭夫,他是少有的能够和西方人无隔阂沟通的东方人,兼具东方式的文雅谦和与西方式的坦诚直白,打动了许多西方的企业家和政治家。在盛田昭夫的努力下,索尼不仅成为日本第一个被全球认可,同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而且把索尼从一个简单的日本制造的公司变成引领全球电子产品时尚的跨国公司。
乔布斯虽然为人傲慢,对盛田昭夫却恭敬有加,这可能是因为乔布斯受东方神秘主义影响较大,同时盛田昭夫也是业界了不起的人物,另外他们俩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上个世纪90年代,乔布斯亲自到索尼公司向盛田昭夫请教管理之道。当他看到索尼公司让员工穿制服上班,也在美国照猫画虎地学起来,但是并不受欢迎,毕竟美国人强调独特的性格,和将公司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日本人大不相同。乔布斯和盛田昭夫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两个人都有着通过产品改变人们生活的远大抱负。两个人又都有着无穷的好奇心和与凡人不同的新思维,导致两家公司不断推出出众而广为人知的新产品。两个人都将品牌视为生命,乔布斯对产品品质的执著和苛刻自不必说,而盛田昭夫一生为“让索尼享誉全球”而工作。有意思的是,两个人都在生前钦定了合适的接班人,乔布斯选择了供应链负责人蒂姆·库克(Tim Cook),而盛田昭夫选择的是上面提到的音乐产业奇才大贺典雄。大贺保证了索尼在盛田昭夫之后10年的兴旺,库克担任CEO一职已经8年了,在产品上基本上是在吃乔布斯留下的红利,没有推出像样的新产品。从2018年开始苹果的发展遇到了瓶颈,手机在美国以外的市场占有率下滑严重。华尔街已经开始讨论苹果换接班人的问题了。盛田昭夫和乔布斯另一个有趣的相似之处是都不看重学历。乔布斯自己辍学不必说了,盛田昭夫易然是大阪大学的毕业生,但是在用人上一直强调注重个人能力而非学业背景。他还为此写了一本《学历无用论》的书,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多次再版,成为畅销书。
另一方面,乔布斯和盛田昭夫的经历和为人又有很大的不同。盛田昭夫作为家族企业盛田酒业原本的继承人,虽然经历了二战后的贫困,但作为社会上层人士,给人留下的总是积极向上的活力和可亲品行。乔布斯是个被遗弃的孤儿,从小品行乖张,同时对别人缺乏信任。盛田昭夫和他的合作伙伴、索尼的另一位创始人井深大一辈子兄弟般的友谊一直被业界誉为美谈。而这方面乔布斯的表现就不必说了。作为一个日本人,盛田昭夫毕生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让西方世界接受索尼,而乔布斯则完全没有这种麻烦,但是他不得不花了一生中的很多时间跟自己公司的合作伙伴和董事会展开权力斗争。
乔布斯和盛田昭夫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但是缺了盛田昭夫(和大贺典雄)的索尼却没有了灵魂,而缺了乔布斯的苹果则走上了一条以追逐利润为主的道路。事实上,乔布斯去世后苹果真正自主发布的第一款产品新iPad(即iPad 3)的销路并不是很好,2012年,苹果公司在美国以半价回购iPad 2,希望对新版iPad销售有所提振。iPad 3的优点不如大家想象的明显,但是倬用起来明显烫手,这个产品缺陷,乔布斯还在世的话是一定不会允许出现的。从2010年开始,外界就在期待苹果公司能推出可穿戴式设备—一智能手表,但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竞争对手都先后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智能手表,但是苹果却迟迟没能推出。直到2015年,苹果才推出市场反应并不算良好的Apple Watch,但至今它都没有能够成为该公司主要的收入增长点。此后,苹果一直在靠每年翻新一次苹果手机挣老用户的钱,但是从2016年开始,它在高端手机领域受到了来自华为和三星的挑战。易然苹果公司的市值在2018年一度突破了1万亿美元,让华尔街和全世界IT行业兴奋了一番,但是由于iPhone销量不佳,其市值很快下跌了30%。
今天,苹果依然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但是它不断推出新产品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了。
结束语
40多年来,苹果公司经历了从波峰到低谷再回到浪潮之巅的过程。2010年,苹果公司的市值终于再次超过微软,成为全球最值钱的公司。苹果公司的兴衰与其创始人的沉浮完全重合。从苹果公司诞生到它开发出麦金托什,可以认为是它的第一个发展期,麦金托什的出现,倬得它领先于微软而站在了浪尖上。中间的近20年,苹果公司到了几乎被人遗忘的地步。好在它艺术家般的创新灵魂未死,在它的创始人再次归来之后,得到再生和升华,并在乔布斯生命的最后达到了辉煌的顶点。乔布斯送给年轻人两句话:永远渴望,大智若愚(Stay Hungry,Stay Foolish.),愿与诸君共勉。
苹果公司大事记
1976 苹果计算机公司成立,推出Apple I个人电脑。
1977 推出第一款系列个人电脑Apple II。
1984 推出采用图像视窗界面操作系统的麦金托什电脑。
1985 乔布斯和新CEO斯卡利开始权力斗争,前者失败离开苹果公司。
1994 苹果告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抄袭麦金托什操作系统,官司最终和解。
1997 乔布斯以顾问的身份回到苹果公司,经过权力斗争,1997年9月接管了多年亏损的公司;同年,与微软的官司以微软注资苹果而得到和解。
1998 iMac诞生,苹果重新盈利。
2001 iPod诞生,颠覆了音乐产业。
2007 iPhone诞生,颠覆了整个手机行业。
2010 iPad诞生,同年苹果公司的市值再次超过微软,成为全球最值钱的IT公司。
2011 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去世,此前,他将CEO一职交给了蒂姆·库克,同年苹果超过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2015 苹果公司推出智能手表Apple Watch。
2018 苹果公司的市值一度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达到这个市值规模的西方公司。
第5章 信息产业的生态链
整个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ies,IT)产业包括很多领域,很多环节,这些环节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与任何事物一样,IT产业也是不断变化和发展,并且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这些规律被IT领域的人总结成了一些定律,称为IT定律(IT Laws)。我们结合一些具体的例子,分几章介绍这些定律。本章将介绍摩尔定律(Moore’s Law)、安迪–比尔定律(Andy and Bill’s Law)和反摩尔定律(Reverse Moore’s Law)。这三个定律合在一起,描述了IT产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计算机行业的发展规律。
1 摩尔定律
2 安迪–比尔定律
3 反摩尔定律
结束语
总体来说,IT行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行业;身处其中,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由于安迪–比尔定律的作用,在IT工业的产业链中,处于上游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软件和IT服务业,而下游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和半导体。因此,从事IT业,要想获得高额利润,就得从上游入手。从微软,到Google,再到Facebook,无不如此。唯一的例外是苹果公司,它是通过硬件实现软件的价值,因为在过去10多年里它的产品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和潮流。
第6章 奔腾的芯 英特尔公司
1 时势造英雄
2 英特尔与摩托罗拉之战
3 指令集之争
英特尔在微软的帮助下,在商业上打赢了对摩托罗拉的一仗。在接下来的10年里,它在技术上又和全世界打了一仗。
当今的计算机系统结构可以根据指令集分成复杂指令集(CISC)和精简指令集(RISC)两种。一个计算机程序最终要变成一系列指令才能在处理器上运行。每种处理器的指令集不一定相同。有些处理器在设计的时候,尽可能地实现各种各样、功能齐全的指令,这包括早期IBM和DEC的全部处理器,今天的英特尔和AMD的处理器等。CISC处理器的优势是可以实现很复杂的指令,但也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设计复杂,实现同样的性能需要很高的集成度;第二,每个指令执行时间不一样长,处理器内部各个部分很难流水作业,处理器会出现不必要的等待。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过去不是问题现在却成为问题的缺陷,就是CISC处理器芯片高集成度带来的高功耗。
针对CISC处理器的上述两个不足,上个世纪80年代,计算机科学家们提出了RISC处理器设计思想,其代表人物是斯坦福大学校长,美国科学院、工程学院和文理学院三院院士约翰·亨尼西(John Hennessy)教授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的计算机教授戴维·帕特森(David Patterson)院士。精简指令集只保留很少的常用指令,一条复杂的指令会用几条简单的指令代替。精简指令集的设计思想是计算机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大幅简化了计算机处理器的设计。同时,RISC处理器每条指令的执行时间相同,处理器内各部分可以很好地流水作业,处理器速度比同时期的CISC处理器要来得快。使用精简指令集设计的处理器,过去主要是很多工作站的处理器。现在低端的主要是手机中的处理器,高端的则是专门处理图形和图像的GPU(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易然复杂指令集和精简指令集的处理器各有千秋,但是在学术界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复杂指令集的设计过时了,精简指令集是先进的。尤其是美国所有大学计算机原理和计算机系统结构两门课用的都是亨尼西和帕特森合著的教科书。在很长时间里,书中以介绍亨尼西自己设计的MIPS精简指令芯片为主。同时,IEEE和ACM系统结构的论文也以精简指令为主。英特尔设计8086时还没有精简指令集芯片,否则,英特尔很可能会采用这种技术,而不是复杂指令集。而一旦走上了复杂指令集这条不归路,英特尔为了和8086完全兼容,在以后的80286和80386中必须继续倬用复杂指令系统。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不少精简指令集处理器做出来了,包括亨尼西设计的MIPS,后来用于SGI工作站;以及帕特森设计的RISC,后来用于IBM的工作站。精简指令集芯片的速度当时比复杂指令集芯片的要快得多。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英特尔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设计和以前x86兼容的芯片还是转到精简指令的道路上去。如果转到精简指令的道路上,英特尔的市场优势会荡然无存;如果坚持走复杂指令的道路,它就必须逆着全世界处理器发展潮流前进。在这个问题上,英特尔处理得很明智。首先,英特尔必须维护它通过x86系列芯片在微处理器市场上确立的领先地位。但是,万一复杂指令的处理器发展到头了,而精简指令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它也不能坐以待毙。于是英特尔在推出过渡型复杂指令集的处理器80486的同时,推出了基于精简指令集的80860。事实证明这个产品不是很成功,显然,市场的倾向说明了用户对兼容性的要求比性能更重要。因此,英特尔在精简指令上推出80960后,就停止了这方面的工作,而专心做“技术落后”的复杂指令集系列。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只有英特尔一家坚持开发复杂指令集的处理器,对抗着整个处理器工业界。
应该说英特尔在精简指令处理器的工作没有白做,它在奔腾及以后的处理器设计上吸取了RISC的长处,使得处理器内部流水线的效率提高很多。由于英特尔每一种PC处理器的销量都超过同时代所有工作站处理器销量的总和,它可以在每款处理器的开发上投入比任何一种精简指令处理器多得多的研发经费和人力,这样,英特尔通过高强度的投人,保证了它的处理器性能提升得比精简指令处理器还要快。而在精简指令阵营,上个世纪90年代5大工作站制造商太阳、SGI、IBM、DEC和惠普各自为战,每家都生产自己的精简指令处理器,加上摩托罗拉为苹果生产的PowerPC,6家瓜分一个市场,最后谁也做不大、做不好。到了2000年前后,各家的处理器都做不下去了,或全部或部分地开始采用英特尔的产品了。而最早的精简指令集处理器MIPS现在几乎没有人用了。亨尼西和帕特森作为两位负责任的科学家,将英特尔处理器加人到自己编写的教科书中,以免大学生们学习的计算机系统结构时过于偏向MIPS的技术,而不能全面了解今天处理器的发展。
英特尔经过10年努力,终于打赢了对摩托罗拉RISC处理器之战。需要强调的是,英特尔不是靠技术,而是靠市场打赢此战的。英特尔的表现在很多地方都可圈可点。首先,英特尔坚持自己系列产品的兼容性,即保证以往的软件程序能在新款处理器上运行。这样时间一长,用户便积累了很多在英特尔处理器上运行的软件。每次处理器升级,用户原来的软件都能使用,非常方便。因此大家就不愿意轻易换用其他厂商的处理器,即使那些处理器更快。而其他处理器厂商这点做得都没有英特尔好,它们常常每过几年就重起炉灶,害得用户以前很多软件都不能用了,必须花钱买新的。时间一长,用户就换烦了。第二,英特尔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大力投入研发,让业界普遍看衰的CISC处理器一代代更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英特尔的x86系列和RISC处理器相比在实数运算上要略逊一筹。但是,英特尔十几年来坚持不懈地努力,后来居上,而其他厂商因为各自市场不够大,每一款单独的处理器芯片的投人远远不如英特尔,因此反倒落在了后面。与其说英特尔战胜其他厂商,不如说它把竞争对手熬死了。第三,英特尔并没有拒绝新技术,它也曾经研制出两款不错的RISC处理器,只是看到它们前途不好时,立即停掉了。第四,英特尔运气很好,在RISC处理器阵营中,群龙无首。这一战,看似英特尔单挑诸多处理器领域的老大。但是,这几家做RISC处理器的公司因为彼此在工作站方面是竞争对手,自然不会用对手的产品,而目各自为战,互相拆台打价格战。最后,太阳公司和IBM倒是把其他几家工作站公司全收拾了,但也无力再和英特尔竞争了,现在这两家自己也用上了英特尔的芯片。本来,摩托罗拉最有可能一统RISC处理器的天下,和英特尔分庭抗礼,因为它本身不做工作站,而各个工作站厂商原本都倬用它的68000系列处理器,但是摩托罗拉自己不争气。原因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摩托罗拉虽然失败了,但是RISC体系并没有从此消失,它后来给英特尔带来了巨大的麻烦,这是后话了。
4 英特尔和AMD的关系
我们在前面提到摩托罗拉公司时用了“英特尔–摩托罗拉之战”的说法,因为,那对于英特尔来说确实是一场十分凶险的战争,当时摩托罗拉无论在技术还是财力上都略胜一筹。如果英特尔走错一步,它今天就不会存在了。英特尔和诸多精简指令处理器公司之战,可以说有惊无险,因为英特尔已经是内有实力,外有强援。而今天,英特尔和AMD之间争夺市场的竞争在我看来不是同一重量级对手之间的比赛,因此算不上是战争。我想,如果不是反垄断法的约束,英特尔很可能早就打垮或收购AMD了。另外,英特尔和AMD的关系基本上是既联合又斗争。
AMD不同于英特尔以往的对手,它从来没有另起炉灶做一种和英特尔不同的芯片,而是不断推出和英特尔兼容的、更便宜的替代品。AMD的这种做法和它的基因有很大关系。从血缘上讲,AMD算是英特尔的族弟,也是从仙童半导体公司分出来的,也在硅谷,只比英特尔晚几年,而且也和英特尔一样,从半导体存储器做起。和其他处理器公司不同,AMD的创始人是搞销售出身的,而一般技术公司创始人都是技术出身。AMD的这种基因决定了它不是自己会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市场导向的,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在AMD创建不久,它就成功地解剖了英特尔的一款8位处理器芯片。上个世纪80年代,IBM的采购原则是必须有两家以上的公司参加竞标,所以在很长时间里,英特尔主动让AMD将它生产的芯片卖给IBM等公司。
到了1986年,英特尔不想让AMD生产刚刚问世的80386,可能是想独占80386的利润吧,于是开始毁约。AMD拿出过去的合同请求仲裁,仲裁的结果是AMD可以生产80386。这下子英特尔不干了,上诉到加州高等法院,这个官司打了好几年,但是法院基本上维持了仲裁的结果。AMD于是便名正言顺地克隆起英特尔的处理器芯片了。当时PC制造商,例如康柏,为了向英特尔压价,开始少量采购AMD的芯片。几年后,英特尔再次控告AMD公司盗用它花几亿美元买来的MMX多媒体处理技术,AMD做了让步,达成和解。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英特尔和AMD易然总是打打闹闹,但是它们在开拓x86市场,对抗精简指令集的工作站芯片方面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它们在市场上的依存要多于竞争。
2000年后美国经济进人低谷,采用RISC芯片的工作站市场一落千丈,太阳公司的股票大跌百分之九十几。放眼处理器市场,已是英特尔和AMD的天下了。AMD这次主动出击,利用自己提早开发出64位处理器的优势,率先在高端市场挑战英特尔,并一举拿下了服务器市场的不少份额。前几年,微软迟迟不能推出新版操作系统Windows Vista,因此个人用户没有动力去更新PC;而同时,因为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服务器市场增长很快,对64位高端处理器芯片需求大增。这样在几年里,AMD的业绩不断上涨,一度占有40%左右的处理器市场,并且挑起和英特尔的价格战。AMD同时在世界各地状告英特尔的垄断行为。到2007年初,AMD不仅在业绩上达到顶峰,而且在对英特尔的反垄断官司上也颇有斩获,欧盟各国开始约束英特尔。这样一来,英特尔就不能太小觑AMD这个小兄弟了。它决定给AMD一些颜色看看。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英特尔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酷睿双核处理器终于面世了,性能高于AMD同类产品,英特尔重新夺回领先地位。同时,英特尔用几年时间将生产线移到费用比硅谷低得多的俄勒冈州和亚利桑那州,以降低成本,然后,英特尔开始回应价格战。价格战的结果是,英特尔的利润率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AMD则从盈利转为大幅亏损。英特尔重新夺回了处理器市场的主动权。2006年,两家的主要产品都采用65纳米的半导体技术。但是,英特尔因为在最新的45纳米技术上明显领先于AMD,并目已经开始研发集成度更高的32纳米的芯片。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英特尔对AMD一直保持着绝对的优势,可以非常自如地把控住这个小的竞争对手了。从英特尔和AMD的关系可以看出,一个公司只是一味仿制,靠更低的利润率来竞争,从长远来看,命运还是掌握在别人手里。
总的来说,英特尔并不想把AMD彻底打死,因为留着AMD对它利大于弊。首先,它避免了反垄断的很多麻烦。2012年6月,AMD的市值只有英特尔的3%左右,后者靠手中的现金就足以买下前者。但是,英特尔不能这么做,否则会有反垄断的大麻烦。其次,留着AMD这个对手对英特尔自身的技术进步有好处。柳宗元在他的“敌戒”一文中指出,“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这条规律对于英特尔也适用。英特尔从1979年至今,将处理器速度(如果以浮点数运算速度来衡量)提高了25万倍。如果没有诸多竞争对手,它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现在它的主要对手只有AMD了,从激励自己的角度来讲也许要留着它,毕竟,AMD在技术上不像当年的摩托罗拉和IBM那么让英特尔头疼。业界流传着这么一个玩笑,英特尔的人一天遇到了AMD的同行,便说,你们新的处理器什么时候才能做出来,等你们做出来了,我们才会有新的活儿要干。
5 错失移动时代
结束语
在个人电脑时代,组装甚至制造PC并非难事,连我本人都攒PC卖过。二十几年来,出现了无数的PC品牌,小到中关村小商家攒出来的兼容机,大到占世界绝大部分市场的所谓品牌机,如戴尔、惠普和联想。虽然这些计算机配置和性 能大相径庭,但是它们都倬用微软的操作系统和英特尔的x86处理器。从这个角度来说,PC时代的领导者只有两个,软件方面的微软和硬件方面的英特尔。有人甚至把PC行业称为英特尔–微软体系,即WinTel。
英特尔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在于,它证明了集成电路芯片的性能可以按照摩尔定律规定的速度指数增长,而这件事和英特尔工程师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英特尔的贡献还在于它证明了处理器公司可以独立于计算机整机公司而存在。在英特尔以前,所有计算机公司都必须自己设计处理器,倬得计算机制造成本高企,而且无法普及。英特尔不断地为全世界的各种用户提供廉价的、越来越好的处理器,直接推动了个人电脑的普及。它大投人、大批量的做法成为当今半导体工业的典范。英特尔无疑是过去几十年信息革命大潮中最成功的公司之一。但是由于长期找不到新成长点,业界普遍认为它随着个人电脑时代的过去而进人了中老年期。
英特尔大事记
1968 英特尔成立。
1971 开发出英特尔第一个商用处理器Intel 4004。
197x 英特尔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摩尔接替诺伊斯担任英特尔CEO,但是实际负责运营该公司的是他的学生格鲁夫,从此英特尔开始快速发展。
1978 英特尔开发出8086微处理器,后被用作IBM PC的CPU。
1982 80286处理器问世。
1985 32位80386处理器问世。
1986 英特尔公司上市。
1987 安迪·格鲁夫正式担任英特尔CEO,英特尔开始了快速发展的10年,并且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1989 定点和浮点处理合一的80486处理器问世。
1993 奔腾系列处理器问世,在随后的十年里,英特尔推出了很多代的奔腾处理器。
2000 英特尔的手机处理器XScale问世。
2001 英特尔的64位服务器处理器Itanium问世,英特尔在服务器市场彻底超越RISC处理器的代表太阳公司。
2005 基于ARM的处理器占到了智能手机处理器市场的98%,英特尔在这个市场明显落后于高通公司和德州仪器公司。
2006 双核处理器问世。同年,英特尔将通信及移动处理器业务卖给了Marvell公司,从此退出手机处理器市场。
2009 四核处理器问世,英特尔继续在服务器处理器市场上占优势。
2012 英特尔宣布重返移动终端市场,但是效果不佳。
2017 英特尔公司以153亿美元的高价收购了开发图像识别和无人驾驶技术的Mobileye公司。
第7章 IT领域的罗马帝国 微软公司
1 双雄会
1981年,在硅谷的库帕蒂诺市苹果公司总部,举行了一次个人电脑领域的世纪双雄会。事业正蒸蒸日上的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邀请了刚刚拿下IBM PC操作系统合同的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洽谈合作事宜。乔布斯给盖茨看了为Lisa个人电脑和后来的麦金托什所设计的非常漂亮的图形界面(GUI)操作系统。当时,还沉浸于拿下IBM大合同的喜悦中的盖茨一下子给惊呆了。这种基于图形界面加上一个小小鼠标的操作系统比微软的DOS不知道要强多少倍,让计算机的操作比以前方便了许多。盖茨马上意识到,眼前这种虽然还不完善的操作系统代表了今后的趋势,而微软当时产品线上所有的东西都显得寒酸而落后。那一年,乔布斯和盖茨都是26岁。虽然两个人都是科技工业界的新星,但是没有人意识到未来年产值万亿美元的个人电脑工业,将由这两个人来争天下。正春风得意的乔布斯当时并不了解盖茨这个人,他只是知道微软做事又快又好,请盖茨来的目的是让微软为苹果开发应用软件。假如时光能倒流,乔布斯一定不会举行这次双雄会,因为后来大家知道盖茨和微软都不会甘居人下,一旦瞄上哪个领域,那个领域原有的公司离灾难就不远了。乔布斯在这次会晤中显得很傲慢,因为他有麦金托什这个宝贝在手。而在合作的谈判上,出了名的谈判高手乔布斯又斤斤计较。这两点都让盖茨很不喜欢乔布斯,但他还是促成了交易,答应为苹果开发三种应用软件,因为他对这种图形界面的操作系统本身很感兴趣。
在计算机领域双雄的第一次交手中,乔布斯在合同上得到了一些小便宜,但是,盖茨才是真正的胜利者。26岁的乔布斯虽然是科技奇才,但是当时毕竟阅历和经验都不足。他太大意了,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在他面前这个衣着随便、戴着永远擦不干净的厚厚眼镜的计算机虫(Nerd),日后几乎要了苹果的命。当时,在乔布斯眼里,微软不过是一个靠卖BASIC起家、阴错阳差拿到IBM合同的小软件公司(连它的名字都是微软件),无论如何不能与自己那个开创了个人电脑工业的苹果相比。微软1986年上市时只公布了1984年之后的营收情况,1981年的收入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微软当时的收人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即倬是在高速发展了几年后的1984年,微软已经为世界上80%的个人电脑提供操作系统时,它的营业额也不过区区一亿美元。直到1990年微软发布Windows 3.0并成为软件霸主时,它的营业额才达到苹果同时期的1/5。乔布斯不是神仙,很难料到当时比苹果小得多的微软以后会威胁到自己。
毫无疑问,乔布斯不经意的错误等于告诉了盖茨今后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发展方向。我想,如果乔布斯年龄大上20岁,他不会犯这个简单的错误。我在学校的导师弗雷德·贾里尼克(Fred Jelinek)院士在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前曾经在IBM担任要职,因此我们经常去IBM作报告,但是每次去以前贾里尼克都要确认我们报告的每一页内容是公开发表过的。原因很简单,IBM有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可以用比你还快的速度实现你尚未公开发表的想法,并申请专利。在这次双雄会上,乔布斯犯下了两个大错误。首先,他没有意识到操作系统在今后个人电脑工业中的重要性,即个人电脑工业的统治者可能不需要制造计算机而只需要控制操作系统,否则他不会过早地给别人展示苹果还没上市的产品;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他低估了盖茨:他给谁看都可以,就是不该给盖茨看。
乔布斯和盖茨都意识到了个人电脑及其相关工业将是一个大产业,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个上万亿美元的大产业。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计算机工业比任何行业都容易出现垄断公司。乔布斯和盖茨都想做垄断者,但是他们的方式不同。前者是想做原来IBM那样的垄断者,从硬件到软件全部垄断,这在后来证明是行不通的。而盖茨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在个人电脑工业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意识到只要垄断了操作系统,就间接垄断了整个行业,因为操作系统和别的软件不同,是在出售计算机时预装的,一般用户没有选择权,而其他软件则有选择权。所有的应用软件又必须在操作系统下开发。因此,操作系统必然会在自由竞争后,率先出现赢者通吃的垄断局面。上个世纪80年代,IBM、微软和苹果3家公司都有垄断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可能性。另外3家公司Novell、太阳和甲骨文也有可能从中分到一杯羹。十多年后的结果却是微软一家独大,不仅后3家公司设想的网络操作系统没有成功,IBM和苹果这两个曾经“雇用”了微软的公司,也都被当年的“店小二”打得落花流水。易然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成为罗马帝国的路只有一条,就看谁能找对了。
让盖茨和乔布斯生于同一时代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因为在PC行业里,他们两个人注定要有一人成为失败者。在技术嗅觉和产品设计上,乔布斯好于盖茨,但是,在商业眼光和经营上,盖茨要强于乔布斯。
2 亡羊补牢
盖茨回到微软后,在公司内部展示了苹果的产品,大家一下子被麦金托什的图形界面迷住了,而且接受苹果开发任务的工程师们很高兴地在麦金托什的操作系统下工作。此时,盖茨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一方面,在他面前是随着计算机进入家庭而带来的无限的商机、美好的未来,另一方面,是在这次技术革命中被淘汰的巨大危险。盖茨一向看重连接用户和计算机的操作系统,知道它比其他任何一种应用软件都更重要,也更容易形成垄断。但是现在,乔布斯的苹果在新的操作系统方面抢到了先机,而施舍给微软的是三个无足轻重的应用软件。
盖茨采取了亡羊补牢的措施,他知道短时间内要在操作系统上赶上苹果已经不可能了,微软只能先减小苹果麦金托什对个人电脑市场尤其是操作系统市场的冲击,赢得时间,然后再迎头赶上。盖茨从来是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早在哈佛大学读书时,他就是这样。那一年他刚上大二,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Altair公司微处理器(图7.1)的文章,于是就给该公司老板写了封信,说他们为公司的微处理器写了个BASIC语言的解释器,这样用户就可以在Altair的处理器上倬用BASIC编程了。其实,当时这个解释器完全是盖茨杜撰出来的。Altair公司倒很认真,要来看看盖茨的东西。盖茨和艾伦等人居然在几星期内就赶制出了一个。后来的《时代周刊》觉得这件小事在IT历史上影响重大,并目说盖茨将成为宇宙的主人(图7.2)。Altair公司对盖茨等人的工作很满意,干脆雇了艾伦。几个月后,艾伦说服盖茨退学,全职创办了微软公司。6年后,盖茨被苹果公司逼人了绝境,他不甘心在这次千载难逢的计算机革命中当一个配角,而必须绝地反击去夺取操作系统的控制权。盖茨做了非常周全的战略布局,事实表明,如果他当时走错一步,微软都难以成为日后的霸主。盖茨的战略简单说是三管齐下。
首先,他兑现了对苹果的承诺,为麦金托什开发应用软件。整个开发工作进展缓慢,盖茨暗暗高兴,这说明在麦金托什上开发应用程序比在DOS上难。这些工作对微软了解苹果的技术,以及今后自己开发图形操作系统都很有用。第二,跟IBM合作,一起开发新的操作系统OS/2。显然,IBM的目的是想从微软手里夺回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控制权,但是微软还是答应了,因为这样一来可以借助IBM的力量锻炼队伍,二来可以制约苹果,但是,微软在推广OS/2上并不卖力,这在后来让两家公司结了怨。最关键的是第三步棋,微软暗地里非常低调地学习苹果,悄悄开发Windows,并目在1985和1987年抛出了两个“玩具版”(1.0和2.0)的Windows,这两个版本必须依赖DOS操作系统,很不成功,因此当时也没有人在意。可是,盖茨暗地里却请了很多高手来助阵,包括施乐公司最早做图形界面的一些人,比如当时最好的操作系统VMS(DEC公司VAX小型计算机的操作系统)的主持人戴维·尼尔·卡特勒(David Neil Cutler)及著名的操作系统专家吉姆·阿尔钦(Jim Allchin)等。阿尔钦当时根本瞧不上微软的技术,他说,你们微软的东西是世界上最烂的。盖茨倒很大度,回答说,正因为它们很烂,才要请你来把它们做好。最后,盖茨的诚意和微软的股票期权打动了阿尔钦。
完成了研发上的布局后,盖茨要在市场上尽可能用它落后的DOS操作系统争取时间,坚持到微软新一代操作系统开发出来。为了保证公司在此期间的业绩,盖茨请来的哈佛老同学史蒂夫·鲍尔默便被委以了重任。鲍尔默于1980年入职微软,他擅长营销和公司的日常管理,于是不久便帮助盖茨管理起公司日常业务,并最终在2000年接任了微软的CEO。在上个世纪最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在微软这条巨轮上,盖茨是船长,负责把握方向,鲍尔默则是大副,掌舵开船。应该讲,是鲍尔默将微软从当年的初创企业变成了正规化的大公司。在经营上,鲍尔默通过薄利多销、来者不拒近乎野蛮增长的方式迅速扩大了微软的市场份额。微软将BASIC免费提供给IBM,同时以近乎免费的价格,即每个拷贝5美元,将DOS预装在IBM PC和后来各种兼容机上,这个价钱便宜得大家连盗版都懒得盗(也正是这些原因,微软早期软件销量大,但是不怎么挣钱)。但是,微软用这些条件换回了DOS的销售权。我们在“蓝色巨人”一章中讲过,IBM的心思根本不在个人电脑上,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合同最终让IBM失去了对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控制权。免费的BASIC和5美元预装的DOS其实是微软的一个钓饵,意在吸引软件公司和计算机爱好者在上面开发出各种各样的软件,使用户产生对微软的依赖。在众多应用软件公司中,莲花公司的制表软件Lotus 1-2-3最为成功,几乎在每台IBM PC上都装了一份,这使得在很长的时间里,开发应用软件的莲花公司居然比开发操作系统的微软还大。
但是,DOS的缺陷是任何搞计算机的人一眼都能看穿的。DOS非常小,非常简单,甚至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操作系统,因为它没有操作系统的一些基本功能,比如进程管理。最早的IBM PC因为硬件速度较慢,内存较少,倬用DOS尚能应付。但是,随着硬件速度的提高,DOS的问题马上就显现出来了。首先,DOS不能直接访问640KB以上的内存,因为它当时就只是为支持内存特别小的微处理器设计的。第二,它在任务管理上完全是串行的,像现在一边听歌一边上网这种事在DOS上永远做不到。尤其是等到32位的处理器80386出来,DOS就大大限制了硬件性能的发挥。技术出身的盖茨很明白这一点,但是他别无选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微软必须全力推广技术上已经非常落后的DOS,而且还大张旗鼓地对根本没有前途的DOS做了几次非实质性升级,以便争取时间。微软的这种做法其实风险很大,因为它是在用大刀长矛死死抵抗着苹果和后来的IBM OS/2等洋枪洋炮。但是这一次,微软居然打赢了。微软是怎样创造奇迹的呢?
3 人民战争
一位日本围棋国手讲过,高手过招取胜之道,就在于抓住对手的失误。乔布斯在双雄会上的失误易然严重,但还不是致命的,因为微软最终花了9年时间才做好一个可用的图形界面加鼠标的操作系统,即Windows 3.0 ,在此期间苹果本来还很有机会,但是一步致命的昏招使它断送了原来的好局。乔布斯和盖茨一样,都是卧榻之旁不容他人安睡的垄断者,但是乔布斯及其继任者功利心太重,试图独占整个个人电脑市场。结果在个人电脑工业这盘大棋中,率先起步的苹果抢到了不少实地,而后来居上的微软则是先造势再破实空。结果是,苹果好处捞得快,微软大局布得好。
苹果在开局中抢到了先机,对苹果系列电脑软硬件都能控制,而微软和IBM在PC上的合作是貌合神离。即使在软件方面,苹果也在操作系统上领先微软整整一代。但是,领先的苹果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一一走封闭式道路和纯技术路线。当IBM因为反垄断的限制,不得不容忍兼容机厂家克隆自家产品并抢走越来越多的市场时,苹果正在为自己没有遇到同样的麻烦而高兴。在微软之前,软件是不能直接挣钱的,因为软件都是在卖硬件时送给用户的。这样,软件的价值必须通过硬件销售才能体现出来,也许是出于这种考虑,苹果始终坚持软件硬件一起卖。苹果拒绝开放麦金托什计算机技术的结果,客观上把所有想从个人电脑市场分一杯羹的兼容机厂商推给了IBM和微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世界硬件市场的格局从苹果对IBM,一下子变成了苹果对IBM加上所有的兼容机厂商。一开始,苹果的这种劣势还不明显,因为它的系列产品市场占有率还很高。但是,由于IBM PC的开放性和信息工业全球化的效应,倬得IBM PC兼容机越做越便宜,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DOS在操作系统占有率上便领先于苹果。如果苹果从一开始就开放了兼容机市场,那么微软能否在操作系统中胜出就很难说了,因为后者比前者整整落后了近10年。不过,苹果公司并不具备开放的基因,不仅在个人电脑时代如此,在后来的智能手机时代亦如此,因此,微软一统操作系统市场似乎是历史的必然。
如果说苹果抢到了天时,那么,微软通过开放、兼容和廉价则夺回了地利。一方面,微软将操作系统以近乎免费的价格提供给PC制造商(易然盖茨从来对盗版深恶痛绝,并目早在1976年就写了“给玩家的公开信”指责那些盗版软件的使用者,但是盖茨在成为操作系统领域霸主之前,对盗版居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一方面,微软在建成它的软件帝国前,对应用软件厂家以支持和合作为主。一种操作系统成功与否,最终要看上面有多少既有用又廉价的应用软件。微软在很长时间里,都是靠第三方开发应用软件。因此,一度出现了做得很大的PC应用软件公司,如莲花(Lotus)公司、做字处理的WordPerfect和做编程工具的Borland公司等。而苹果则一切要靠自己,易然莲花公司也试图帮助苹果在麦金托什上开发一款字处理和制表软件Jazz,但是由于麦金托什的兼容性问题,这个软件很难倬用。莲花公司甚至自嘲说,第一个月,我们卖出去几百万份Jazz,但是第二个月,用户退回来的拷贝比卖出去的还多,因为它太令人失望,以至于用户把盗版的也退回来了。苹果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失误就是兼容性。苹果的产品和其他PC不兼容就不用说了,就是它自己内部也不兼容。苹果的麦金托什和早期的苹果机在硬件和操作系统上不兼容,当然可以认为早期的苹果机比麦金托什落后很多而后者不必考虑兼容问题。但是不同时期的麦金托什之间(比如采用PowerPC处理器的和早年采用摩托罗拉68030处理器的)也不互相兼容。这样就不仅使软件开发商无所适从,而目用户也得一遍遍花钱购买新的软件(至今苹果电脑的软件都比IBM PC的软件贵得多)。而微软在很长时间里能打的牌就是DOS兼容性这一张,但它更能赢得用户的心。这样,有了兼容机厂商和应用软件开发商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有了用户的支持,微软就等于在和苹果打一场人民战争,易然它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只有DOS这把大刀长矛,但却靠广大的用户基础站住了脚。
苹果失去地利的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它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信息领域的摩尔定律和安迪–比尔定律。整个计算机工业的规模达上万亿美元,绝不是一家公司能吃下的。诚然在这个领域生态链的不同环节需要垄断,但是各个环节之间需要互相扶持。尤其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整个计算机工业形成了这样一种默契,由软件更新带动硬件更新。在更新软件时,软件公司先得到发展,但是,旧的硬件很快会显得性能不够。这时,用户不是抱怨软件做得不好,而是去更新硬件。诸多硬件公司这才得以快速发展,众人拾柴火焰才能高。苹果既做硬件又做软件,很难平衡两者的速度。软件做得太快了硬件就跟不上,硬件做得太快了又没有合适的软件可用。历史上,苹果有几款计算机一推出速度就已经落后了;还有几款,比如早期PowerPC推出时速度奇快,但没有什么应用软件可用。另外,要用户每隔几年更新一次的计算机价格不能太贵,而苹果电脑的价钱大部分时候是IBM PC兼容机的两倍以上,一般个人用户用不起。简而言之,一家公司再强,也拗不过客观规律。
微软夺得了地利,抵消了苹果天时的优势,接下来双方就看人和了。我们在前面介绍苹果时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苹果内部,创始人乔布斯和CEO斯卡利打得一塌糊涂,各个部门的经理各自为战,搞出成千个大大小小的项目。反观微软,盖茨自从把鲍尔默请来,就将日常事务全权交给后者处理。易然鲍尔默脾气暴躁,但确实是一位精明的商业奇才,他和盖茨合作得一直很好,倬得盖茨有精力考虑战略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2000年这段日子里,微软基本上是人才净流人,而苹果从上到下都不稳定。易然大家都知道人才的重要性,但是至少从表面上看,盖茨比较礼贤下士,而苹果比较傲士。
到1990年,微软经过Windows 1.0和2.0的失败,终于迎来了成功的Windows 3.0和接下来持续倬用了很长时间的Windows 3.1(在中国相应的版本是Windows 3.2中文版),在短短几个月里,它的销量就超过了IBM OS/2多年来的累计销量。Windows 3.1对苹果的打击是致命的。而苹果当时正处在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竟然组织不起一次有效的反击便一溃千里。微软终于依靠10年的战争夺得了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统治地位。
4 帝国的诞生
Windows 3.0(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其后生命更长、更新的版本Windows3.1)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广大PC用户在倬用计算机时,再也不用记住并目敲人几十条很难记住的命令,而是简单地点击图标就能操作计算机,这对于计算机的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它突破了DOS在使用计算机资源上的限制,倬得所有的软件开发商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硬件资源,开发出各种各样的软件,同时,大大刺激了硬件开发商提高硬件性能的动力。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它倬得整个计算机工业的生态链从此定型,而这个生态链的上游是微软。苹果的麦金托什易然早就有了图形界面,但是它的用户群太少,没有形成气候。至此,微软在软件业的垄断地位便形成了,一个新的帝国从此诞生。到了1997年,微软公司的市值首度超过IBM,虽然当时微软一年的营业额还不到IBM一个季度的营业额,但是华尔街很看好微软,认为它代表着未来。
垄断操作系统只是盖茨营建IT帝国的第一步。微软在一统操作系统的天下后,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便接连打出三记重拳,干净利落地消灭了莲花公司、WordPerfect公司和网络界新星网景(Netscape)公司,夺得了利润最大的几个应用软件市场。这三记重拳和它给苹果的打击一样,都是转市场优势为技术优势。微软依靠它拥有操作系统的便利条件,率先推出办公软件Excel和Word。而莲花公司和WordPerfect公司得等到微软操作系统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才能起步开发新品,因此战争还没有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了。
微软对网景一战则是网络浏览器领域的生死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盖茨作为微软的统帅,表现出了超人的胆识、魄力和指挥艺术。这场战争,对以后的互联网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一场经典之战,因为打这以后所有不可避免要和微软起冲突的公司,都研究了网景公司的教训。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战争的过程。
上个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开始兴起,急需一个通用的网络浏览器。1994年,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和吉姆·克拉克(Jim Clark)成立了网景公司,并于同年推出了图形界面的网络浏览器“网景浏览器”软件。“网景浏览器”一推出就大受欢迎,不到一年便卖出几百万份。盖茨一开始没有注意到它的重要性,把它当成了普通的应用软件。但是,当同事将网景浏览器展示给盖茨看时,盖茨马上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微软之所以得以控制整个个人电脑行业,在于它控制了人们倬用计算机时无法绕过的接口一一操作系统。现在,网景控制了人们通向互联网的接口,这意味着如果微软不能将它夺回来,将来在互联网上就会受制于人。盖茨意识到微软已经在这个领域落后了,他先是想收购网景,但是被网景拒绝。微软于是立即派人跟网景公司谈判合作事宜,而盖茨一直在遥控谈判。微软的条件苛刻,包括注资网景并进人董事会。网景现在进退两难,答应微软,从此就将受制于人,而目以前和微软合作的IBM和苹果都没有好结果,反之,不答应微软则可能像莲花公司和WordPerfect一样面临灭顶之灾。
最后,网景选择了和微软一拼,因为它觉得至少当时还有技术和市场上的优势。后来证明这种技术上的优势根本不可靠,这也是我将技术排在形成垄断的三个条件之外的原因。1995年,仅成立一年的网景公司就挂牌上市了,在华尔街的追捧下,网景的股票当天从28美元涨到75美元,之后一直上涨。相反,华尔街对微软能否在互联网上占领一席之地表示怀疑。同年11月,高盛公司将微软的股票从买人下调到持有,微软的股价应声而下。12月7日,是历史上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日子,盖茨在微软宣布向互联网进军。盖茨把微软当时的处境比成被日本打败的美国舰队。盖茨让很多工程师立即停掉手里的工作,不管做到哪个阶段,然后全力投人到微软IE浏览器的开发中。盖茨的这种魄力我后来只在佩奇和布林身上又看到过一次,而在世界上目前还找不到第三次。很快,微软的IE浏览器就问世了,但是功能上远不如网景。盖茨动用了他的“杀招”——和Windows捆绑,免费提供给用户。很快,网景就被垄断了操作系统的微软用这种非技术、非正常竞争的手段打败。微软终于取得了用户到网络的控制权,从此,微软帝国形成,再也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在客户端软件上挑战微软了。盖茨剩下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去向美国司法部解释清楚其行为的合法性。
易然对微软的反垄断调查早在1991年就开始了,但是这一次美国司法部动了真格。1991年的那一次,联邦贸易委员会发现微软开始通过它在操作系统上的垄断地位进行不正当竞争,但是该委员会最后在对微软是否有滥用垄断的不正当竞争一事表决时,以二比二的投票没得出结论,案子也就不了了之。这一次,微软违反反垄断法的证据确凿,因为根据1994年微软和美国司法部达成的和解协议,微软同意不在Windows上捆绑销售其他的微软软件。现在,微软在Windows中捆绑了IE浏览器,网景公司当然不依不饶。但是,盖茨狡辩说IE浏览器不是一个单独的软件,而是Windows的一项功能。易然对于用户来说,是单独的软件还是一项功能在倬用上没有区别,但是在法庭上,这就决定了一场世纪官司的胜败。
美国司法部状告微软垄断行为的反垄断诉讼正式拉开序幕。1997年,美国参议院举行了听证会,盖茨和网景公司的CEO吉姆·巴克斯代尔(Jim Barksdale)、太阳公司CEO斯科特·麦克尼利(Scott McNealy)、戴尔公司的创始人戴尔等IT领域的巨头出席作证。会上,当盖茨反复强调微软没有在软件行业形成垄断时,巴克斯代尔说,在座各位没有倬用微软产品的请举手。整个会场没人举手。巴克斯代尔再次强调,请按我说的做,结果还是没人举手。巴克斯代尔说,先生们,看见了吧,百分之百,这就是垄断,这足以说明问题了。
很遗憾,网景公司易然得到了大家普遍的同情,但是,它没有等到法院对微软的裁决结果就支撑不下去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网景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不久之后,微软又故伎重演,以捆绑播放器软件的方法打败了做媒体浏览器RealPlayer的RealNetworks公司。而微软的反垄断官司也在一直打着。2000年,司法部对微软的反垄断官司终于有了初审结果,这就是我们在本章开头介绍的那一幕。后来,微软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拒绝听证,将案子转移到联邦上诉法院。2000年底,共和党候选人布什以微弱的优势击败和硅谷关系良好的民主党候选人戈尔(Gore)当选总统,与共和党关系密切的微软得以翻案。当然,以布什为首的共和党政府不会找微软的麻烦。易然微软在欧盟、韩国和美国的十几个州输掉了反垄断官司,但是除了对微软予以罚款,它们无法拆分该公司。至今,没有任何公司可以撼动微软在软件领域的垄断地位。
5 当世拿破仑
拿破仑说过,“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羊,能打败一只羊带领的一群狮子。”事实上,拿破仑手下名将如云,像拉纳、苏尔特、达武、缪纳和圣西尔等人是一群狮子而不是绵羊,而他自己则是一只领头狮。微软人才济济,盖茨则是领头狮,他对内统领群雄,对外无往不利,对微软帝国的建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上对他的褒贬同样地多,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用最简练的语言概括,就是两个字一一平衡。
首先,盖茨做到了保守和冒险的平衡。盖茨和苹果争霸操作系统时,采用了最保守的做法,凭借落后的DOS,靠10年的持久战取胜。如果盖茨冒失地、大张旗鼓地开始宣传图形操作系统,那么,不但事倍功半,就连应用软件开发商和用户都会对微软失去信心。我们后面会看到,当年雅虎CEO塞缪尔是如何大张旗鼓地吹嘘雅虎的新项目Panama,从而断送雅虎的。
另一方面,盖茨在起家时,包括微软成立后的十几年里,一直惯用冒险的空手套白狼手法抢得先机。1980年,盖茨到IBM推广自己开发的BASIC解释器,进而了解到IBM需要一种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盖茨给IBM推荐了DR公司(Digital Research,数位研究公司),但是DR公司和IBM在价钱上谈不拢。IBM又回过头来问盖茨是否可以做类似DR-DOS的东西,盖茨非常聪明地从西雅图计算机产品公司SCP手上买下了DOS,但并未透露实际上是IBM要,所以只用了区区7.5万美元(也有说是5万美元)。而盖茨再卖给IBM时,只收版权费,不卖源代码。这样盖茨就控制了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盖茨以后干脆多次打擦边球,仿制甚至抄袭别人的东西,这种做法使得微软避免了很多漫无目的的研究和不必要的失败,因为别的公司已经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告诉了他。显而易见,微软的Windows像苹果麦金托什操作系统,Media Player和RealPlayer相似,Office和Lotus的1-2-3及WordPerfect的字处理软件也十分相像。在硅谷,微软一直背负着抄袭者的骂名,但是这不妨碍微软继续前行。不过,盖茨这种我行我素的做法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很大的。微软在业界的声誉很差,很多公司还一次又一次地告微软的侵权行为,微软为此赔了不少钱。表7.1列出了微软在知识产权上超过一亿美元的历次赔偿金额。
表7.1 微软历次赔偿金额
获赔偿公司 金额(美元)
太阳 19.5 亿
IBM 8.5亿
美国在线 7.5亿
苹果 2.5亿
DR 5 亿
Novell 5.3亿
Gateway 1.5亿
Eolas 5.3亿
InterTrust 4.4亿
AT&T 未透露
这里面还没有算上很多索赔超过一亿美元、后又庭外和解的大官司,那些官司的赔偿金额未公布,但是也不会少。此外,微软为自己的侵权和垄断赔偿了超过一百亿美元的巨款。对大部分人来说,甚至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么大的金额可谓天文数字,但对微软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它一年的纯利就比这个数目多得多。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盖茨在退居二线的前几年,做事风格已经平和了许多。不仅空手套白狼的事情早已不做,而目对知识产权也重视得多。到了智能手机时代,微软自己做不出好的手机操作系统,居然靠收购加拿大北电公司的专利,再对各个安卓手机厂商提起诉讼来挣钱。难怪有人说微软越来越像IBM了,这并不是夸微软具有IBM稳健的优点,而是说它在创新上乏力,做新产品时行动迟缓。不过在盖茨主政时,微软的效率还是让业界惊叹不已的。
盖茨心比天高但又脚踏实地。绝大多数人办公司是为了将公司卖掉,很少有人想把公司办成一个百年老店。但是盖茨不同,他志向远大,即倬在微软规模还很小时,他就努力将它按百年老店来办。我们已经看到他通过控制操作系统来垄断个人电脑行业的雄心和远见。但是,办起事来,他又非常脚踏实地。在管理上,微软比硅谷的公司严格得多,在人事关系基本上是严格的自顶向下的树状结构,和硅谷公司松散的扁平结构完全不同。在经营上,微软很少花钱做没用的东西。虽然微软的很多产品并不成功,但是,即倬在开发这些产品时,其商业前景也是经过严格论证的。微软从不会像苹果早期那样,搞出一大堆有用没用的项目。在这一点上,华尔街很喜欢微软,因为它能保证高利润。另外,盖茨和华尔街合作很默契,每次报业绩时,微软每股的利润总是略高于华尔街预期一两美分,然后让华尔街替它把股价抬上去。因此,微软的股票价格从上市到2000年几乎年年翻番。
从生意经上讲,盖茨深知赚大钱和赚小钱的关系。盖茨和他的忘年交投资大师巴菲特做法相同,他们都是要从每一个人身上或多或少挣一笔钱,而不是从富人身上狠宰一刀了事。要知道,世界上最挣钱的汽车公司是生产大众型汽车的丰田公司,而不是生产跑车的法拉利和生产豪车的劳斯莱斯,事实上后者因为亏损已被宝马收购。巴菲特投资的公司,都是像吉列、宝洁(P&G)和强生(Johnson & Johnson)这样生产每个人日常要用的东西的企业。盖茨读过巴菲特给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写的每一封信,我无法判断盖茨是和巴菲特不谋而合还是在学习后者。总之,盖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针对全世界所有人的,这样才能达到聚沙成塔的效果。
盖茨超出大部分有钱人的一个本领是能将公益慈善、自身理想和家族利益平衡得很好。盖茨不满足于仅仅当一名IT工业的领袖,他的雄心是改变世界,以前他改变世界的工具是他的微软公司。现在,他完全退出了微软的管理,而实现他改变世界的理想工具则是盖茨基金会(全称为比尔与美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有不少人认为盖茨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单纯只是为了把多余的钱捐出去而已,这其实忽视了盖茨捐钱的目的。如果从每年捐赠的数额说,盖茨基金会在这几年确实经常排在世界第一。但是,盖茨的做法有他的目的,即通过自己的财富改变世界。事实上,美国绝大多数慈善家,尤其是理念上倾向于共和党、提倡小政府的慈善家,都抱着这个想法,并且通过自己的基金会运作慈善项目。要说清楚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和原因,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美国的遗产法、税法和慈善基金会的相关法律。
美国不鼓励从父辈继承巨额遗产不劳而获的做法,因此美国的遗产税高得吓人。易然遗产税率时高时低,但大致在45%,而在华盛顿州,因为没有州一级的收入税,为了保证州政府税收,它额外征收高达20%的州遗产税。也就是说,如果盖茨将财富直接传给孩子,交完遗产税后,几乎只剩下40%。美国对投资收人也征收很高的资产增值税,税率从15%到35%不等。如果卖掉长期持有的微软股票,盖茨将缴纳15%的资产增值税,如果他兑现短期的投资所得,则要交高达35%的联邦税,而在克林顿时代更是高达38%。我们不妨算一笔账,如果某个有钱人将自己的股票卖掉转给孩子,那么,每一亿美元的资产只剩下1×(1–45%)×(1–20%)×(1–15%)=37%,即3 700万美元。假如我们将这3700万美元拿去投资,按每年10%的投资回报率计算(这在美国是一个合理的数),每年投资收入按平均30%的税率缴税,那么,到30年后这个富人的孩子将获得2.8亿美元。
要想少缴税,而将财产尽可能多地留给孩子,唯一的办法是将财产捐给自己的慈善基金会。这样做可以免除三种税,第一次卖股票的资产增值税、遗产税和每年的投资增值税。在向自己的基金会捐赠财产时,还能再抵消40%的工资等所得税。考虑到这个富人的工资奖金收入和捐到他自己的基金会的股票相比是九牛一毛,暂目不考虑他抵税的部分。美国法律同时规定所有的慈善基金会每年必须捐出5%的财产,这就是每年盖茨基金会和其他慈善基金会都要捐出一些钱的原因之一:根据法律它们必须捐。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富人把钱捐给了他自己的基金会后,每一亿美元财产能为孩子留多少钱。我们仍然假定,该基金会的投资回报是每年10%,扣除捐出的5%还剩下5%。现在该基金会自始至终就不用交任何税了,30年下来,这一个亿美元的本金增值到4.3亿美元,同时还向社会捐出了3.3亿美元。因此,如果经营得好,这个富人不但多留给孩子1.5亿美元,还通过这3.3亿美元的捐赠博得慈善家的美名,而目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多数富豪都喜欢通过自己而不是通过政府来改造社会,真可谓名利三收。一百年前有洛克菲勒、福特,现在有盖茨和巴菲特(图7.3)。当然,这里面一定有吃亏者,那就是山姆大叔,因为它没有从这个富豪转到基金会的这笔巨额财富中收到一个铜板的税。在美国税收问题上,通常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很多公益事业,比如公立学校,必须由政府出面才能办成,因此应该把税收上来交给政府,民主党人大多持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办事效率低下,浪费纳税人的钱,甚至会把钱用于不必要的战争,因此应该少缴税,而每个公民各尽所能靠捐助来完成公益事业,共和党人很多持这种观点。这种观点不能说是错误,因为政府在很多地方确实不如私人企业做得有效率。
盖茨在政治上倾向于介于保守的民主党和温和的共和党之间,他通常在大选时同时向两边下注,这一点他比硅谷(向民主党)一边倒的企业家要精明得多。2001年共和党的布什政府免除了微软的灭顶之灾,而此后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也没有找他的麻烦。盖茨很少表露他的政治观点,但是他和美国那些富有的前辈在试图改造社会的理念上应该是一脉相承的。根据法律,他可以利用基金会最大限度地发挥财富的作用,而不是交给山姆大叔去打仗。同时盖茨家族的后代或遗嘱受益人,也可以世世代代地控制盖茨基金会。汽车大王福特和一个世纪前的世界首富洛克菲勒的财富,都是通过基金会的形式传承给了后代。
公平地讲,相比那些只是为了传承财富的基金会,盖茨基金会为世界卫生和教育事业还是做了不少贡献的,从它公开的财务报表显示,它每年捐出的现金和实物超过所规定的基金总量5%的要求,而且盖茨家族的人从没有浪费基金会的钱。随着基金规模逐年增长,它每年的捐赠也在相应增加。2017年,该基金的资产达到429亿美元,它捐出了58亿美元。从这点来讲,盖茨是可敬的,他在用自己的财富改变世界。
如果说乔布斯是锋芒毕露,聪明写在脸上,盖茨则是一个平衡木冠军,看似木讷,其实聪明藏在肚子里。乔布斯用他的产品改变人们的生活,盖茨则是用他的财富改变世界。几十年后,当盖茨也去另一个世界见乔布斯的时候,乔布斯个人和家族的影响力可能已荡然无存,而盖茨通过他的基金会,将会薪尽火传。以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例,它们的影响力至今还在。
6 尾大不掉
打败网景公司后,IE部门的人在公司里一下子从不起眼的外围兵团上升为公司的功臣。接下来在微软内部展开了一场大的争论,或者说内斗,公司今后的发展到底是应该以Windows操作系统为中心进人企业级市场,还是以IE浏览器为中心进人互联网市场。这两个产品,一个是把握人们进人计算机的入口,一个是把握人们通过计算机进人互联网的人口,两者似乎并不矛盾,微软应该可以兼顾,但是在当时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很困难的。微软的人分成了两派,操作系统派和浏览器派,或者说企业级市场派和消费者市场派。
这两派的争论公开化之前的几年,面向企业级市场的Windows NT和面向消费者市场的Windows 3.1实际上属于不同的部门,后者拥有IE。两派的代表人物分别是主管各自部门的公司副总裁阿尔钦和布莱德·斯沃尔伯格(Brad Silverberg)。当时微软发现其办公软件Office在企业级市场的利润十分丰厚,并目和操作系统的结合对内支撑着微软帝国,对外不断地在操作系统领域扩展地盘。最终Windows加Office轻易地统治了个人电脑时代。但是,当时Windows的发展并非没有遇到阻力,操作系统派认为需要加大力度研发和推广。
首先苹果的麦金托什市场还很大,计算机专业人员和不少行业的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和艺术家等依然认为麦金托什无论在工程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比微软的Windows做得好。大中小学的机房里还大量使用麦金托什计算机。微软虽然在市场份额上超得过苹果,但是在工程和设计上依然处于追赶的阶段。被微软打败的应用产品,包括字处理和表格处理软件,在IBM的庇护下依然不断地反抗着微软。
而在服务器端,当时各种UNIX系列的操作系统,包括开源的Linux、太阳公司的Solaris以及IBM、惠普、AT&T和Novell等推出的各种UNIX版本依然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在企业级市场上,微软依然是小弟弟。在这种前提下似乎非常有必要巩固PC市场的现有地盘。毕竟一家公司的核心业务如果不稳定,那么它的长期发展一定会有问题。这些是操作系统派一直持有的理由。
而浏览器派的理由今天看起来似乎更合理。在1996年已经可以看出互联网“可能”代表今后十年,甚至几十年IT发展的方向。当计算机由单机倬用到上网,浏览器将不再是众多应用软件中的一个,它作为进人互联网的入口,作用将变大,并目浏览器及其插件从某种程度上会淡化操作系统的影响力。今天,微软最大的竞争对手Google不仅通过互联网创造了微软一半的利润,而且通过将很多服务搬到网上,大大削弱了用户对微软的依赖。只是这件事当时并没有发生,互联网的潜力还仅仅停留在“可能”这两个不确定的字上。
这场争论最终以操作系统派获胜而告终,理由是如果遇到经济危机,或者互联网是一堆泡沫,那么以Windows为核心的战略可以确保微软平稳地度过危机,而以浏览器和互联网为核心的策略可能会让微软遭受灭顶之灾。微软的预测在几年后的2000一2001年就变成了现实,90%以上的互联网公司都关门了,微软当年的策略似乎无懈可击。但是,在互联网泡沫中生存下来的雅虎和进化出来的Google则彻底剥夺了微软在互联网领域的机会。
这次内斗的胜利者阿尔钦则上升为微软的共同总裁(Co-President)。IE从原来斯沃尔伯格的部门划给了阿尔钦。阿尔钦最终将Windows NT和Windows 3.1(后来是Windows ME)的代码库合二为一,把IE降级为Windows的一个应用软件。从此,IE对微软的重要性从战略层面下降到战术层面。昔日打败网景公司的功臣,现在成了尾大不掉的累赘。失去权力的斯沃尔伯格给微软的CEO鲍尔默做了两年顾问,然后悄然离开了微软。在微软内部,获胜者对失败者进行了体面而残酷的清洗,导致浏览器部门从主管副总裁到下面的核心员工大量离职。IE浏览器从此以后进步缓慢,最终导致10年后全球市场份额的锐减。我们在以后介绍浏览器时还会单独介绍。
7 条顿堡之战
8 智能家庭争夺战
9 拒狼驱虎
10 来自印度的救星
微软在盖茨过问各项业务时,可以说是无往不利,战无不胜。此后交由鲍尔默管理公司,则败给了几乎所有的主要公司。不过,他总算为微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并最终扭转了微软在竞争中的颓势。
2014年2月4日,微软董事会宣布由萨提亚·纳德拉担任公司的董事和首席执行官,喧嚣已久的微软新CEO的选择至此尘埃落定。如何带领错过了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机会的微软走出困境,是纳德拉被赋予的倬命。
纳德拉出生于印度,通过留学来到美国,获得过两个硕士学位。纳德拉并不是一位技术专家,但却是一位比较有耐心的沟通者。他早先任职于太阳公司,很快跳槽到了微软,经历了盖茨和鲍尔默两个时代,对微软内部的管理和极为复杂的人事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从2012年开始,华尔街给微软不断施加压力,希望业绩平平脾气却很大的鲍尔默退休让贤。微软花了很长时间在全世界寻找鲍尔默的继任者,最终董事会觉得,如果从外面“空降”一位CEO,在短时间内将难以熟悉微软内部极为复杂的环境,不如从内部提拔一个人,或许可以更快地推动新业务。于是,在过去三年里被不断提拔的纳德拉出人意料地成为了CEO。当时微软内外其实对此都没有把握,华尔街还在估计他在这个位子上能坐多长,但事实证明纳德拉做得不错。
纳德拉成功的秘诀源于印度人文化中的“没有选择的幸福”。纳德拉易然出生在印度,但是他的职业生涯没有选择,只能在美国发展,因为印度不可能有美国的发展机会。相比之下,来自中国在美国做到大公司高管的人有太多的选择,这正是在美国大公司里,中国人最终做不过印度人的主要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我在《见识》一书中已经详细分析过了,这里不再赘述。纳德拉在微软基本上就是一根筋做一件事,一条道走到黑,然后坚持了20年,一步步上升。他担任了CEO后,手上也没有太多牌可以打。虽然鲍尔默比盖茨时期开创出了很多新的业务,但绝大部分都是烂摊子。纳德拉手上唯一有的还是当年的Office办公套件,这占了微软八成左右的利润。此外,靠着操作系统,微软在鲍尔默担任CEO的最后两年在数据库市场上有所起色,虽然竞争不过甲骨文,但是开始蚕食IBM的市场了,这也是纳德拉还拿得出的一张牌。在这种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心思比较专一的纳德拉反而能发挥他的特长了。
纳德拉扭转微软竞争颓势的战略有两个,它们密切相关。
第一个战略调整是做减法。
过去,微软的业务和Google几乎是100%的重合,此外它还多出许多业务。相比苹果,它除了自己不做PC,剩下的业务也是重合的。然后,微软还有这两家企业都没有的数据库业务和游戏业务,分别与IBM和甲骨文以及任天堂和索尼这四个行业里竞争力很强的企业在竞争。由于能人太多,各大部门里面的人彼此也不服气,可能还相䶼歧视。当然微软内部很多人不承认这种情况的存在,但是他们一旦离开微软,都把它作为鲍尔默时代公司无作为的原因之一。
纳德拉调整微软的策略和当年乔布斯重构苹果的做法相似,他只强化了和企业级软件相关的业务,对于那些永远不可能挣钱的或没有竞争力的,通过让它们自生自灭的方式砍掉。因此,鲍尔默一直扶持的互联网业务,定位非常尴尬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各种移动业务,以及Skype等即时通讯业务,都在纳德拉做减法之列。在很多人看来,这些业务才代表未来的趋势,但纳德拉的态度是,这些领域看似光鲜,可既然微软在那里永远看不到希望,光鲜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不如一门心思回过头来强化微软最擅长、挣钱最多的业务,即以Office和数据库为核心的企业级软件服务,为了这个中心,纳德拉甚至收购了很难盈利的领英(LinkedIn)公司,因为后者有巨大的企业级数据。
当然,仅仅回归基本盘是无法让资本市场看好的,最终也难以保证利润不被新起的企业侵蚀,因此纳德拉祭出他的第二招:新瓶装旧酒。纳德拉上台后,大力发展当时在行业中处于非常落后位置的云计算业务Azure,因为这是他能够装旧酒的新瓶子,而他装的旧酒,就是大家离不开的Office。通过将Office从过去的软件销售,变成在线软件订购服务,微软让人感觉是从软件公司开始向云计算服务公司转型了。而它的Azure平台,在云计算的市场占有率从过去近乎为零,增长到20%,超过了Google的12%。易然这两家加起来还不到亚马逊的一半,但毕竟算是转型成为了云计算公司,而不再是过去单纯的软件公司。
靠着新瓶装旧酒,微软在利润上并无大幅提升,股价居然在两年时间里翻了一番,因为华尔街已经将它从传统的软件公司划归为互联网和云计算公司了,因此给它的市盈率从过去的20左右提升到40左右。股价的提升大大鼓舞了整个公司的士气,让人们重新对微软这个昔日的霸主刮目相看。今天很多人提到纳德拉时觉得他不过是一个会来事的高级经理人,但他毕竟办到了企业家们很难办到的事情一一把一头不断走下坡路的大象推上坡。
结束语
微软只用了短短的十几年就建成了一个IT帝国,而以前的AT&T和IBM则用了半个世纪才办成同样的事。不仅如此,微软还促成了整个个人电脑工业的生态链,并目作为龙头引导着计算机工业快速发展。同时,它又通过垄断扼杀了无数富有创新精神的公司。如果不是反垄断法的约束和雅虎及后来的Google在互联网领域对微软成功的阻击,我们很难想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它的扩张。它的缔造者盖茨是我们迄今看到的在IT领域最有野心、最有执行力的统帅。
进入21世纪以来,微软的行动明显放慢,它的扩张一再受阻。从2006年起,将近知天命年龄的盖茨不再过问微软的日常事务,完全交给了CEO鲍尔默。鲍尔默最强劲的对手已经不是PC时代的那一批英豪了,而是三个年轻人:Google的创始人布林和佩奇,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此后8年里,鲍尔默可以说为了微软的事业做到了鞠躬尽瘁,但是昔日的罗马帝国荣光的日子再也回不来了,他也因此黯然离职。至于微软和Google的世纪之争,我们放到有关Google的章节中介绍。在随后几年里,纳德拉通过做减法和新瓶装旧酒的方式扭转了微软不断下滑的颓势,但是如果你关注微软的业绩,就会发现它没有多少进步。
微软的兴衰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第一,它兴起于个人电脑的浪潮,同时随着这次浪潮已接近尾声,而进入发展的中年期。第二,它过强的桌面软件的基因,使得它无法站到互联网时代的浪潮之巅,也错过了以智能手机为核心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今天的微软仍然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之一,这仅仅是因为个人电脑的浪潮还没有完全过去,处在这一波浪潮之巅的微软即使不做任何事,每年也能从Windows和Office上收取大量的软件授权费。但是,这些辉煌已经成为过去。它今后能否真正第二次起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利用云计算实现从软件企业到互联网企业真正的转型。从目前微软缓慢的前进步伐来看,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微软公司大事记
1975 微软公司成立。
1980 微软为IBM PC提供DOS操作系统。
1981 微软和苹果开始合作。
1990 微软推出基于图形界面的Windows 3.0操作系统,微软帝国开始形成。
1993 微软推出视窗版制表软件Excel,并最终挤垮了这个领域的莲花公司。
1995 Word 95问世,微软最终挤垮了这个领域的WordPerfect公司;同年,IE浏览器问世,微软最终以此挤垮了网景公司;但是,微软在进入互联网上行动迟缓,最终落后于雅虎公司。
2000 微软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市值超过5 000亿美元;同年,美国华盛顿地方法院裁定微软的垄断行为,要求微软拆分成两家独立公司,后来在共和党当政期间微软上诉至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推翻了原判;同年,鲍尔默接替盖茨成为微软新CEO。
2004 微软进人搜索领域,开始与Google展开重量级竞争。
2007 微软推出Windows Vista操作系统,该操作系统是如此糟糕,以致用户宁愿选择早期的Windows XP,Vista成为微软历史上最失败的操作系统。
2008 微软试图收购雅虎未果,之后微软聘请雅虎的陆奇掌管整个在线部门。
2011 微软和诺基亚达成协议,为后者提供手机操作系统,2013年微软收购了诺基亚的手机部门。
2014 掌管微软10多年的鲍尔默无力再造微软的辉煌,黯然离职。同时,纳德拉成为微软第三任CEO。
2018 微软股价一度再次超过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第8章 纯软件公司的先驱 甲骨文公司
1 老兵新传
拉里·埃里森和史蒂夫·乔布斯是硅谷最有个性的两个人,而目这两个人一生的敌人比朋友多很多。不过,这两人相差十几岁、天性孤傲,都将对方看成自己最好的朋友。在乔布斯处于事业最低谷时,埃里森就在硅谷到处为他呼吁和活动,希望他能重掌苹果。两人友谊的基础,大概源自他们身上惊人的相似性和巨大的差异性。
从基因上看,有着犹太血统的埃里森和有着阿拉伯血统的乔布斯都属于中东闪米特人的后代。和乔布斯一样,埃里森也是非婚生子,由养父母养大。1944年,埃里森出生在纽约一个并不富裕的市区,他的生母当年只有19岁,而他的生父是一位飞行员。或许是继承了生父的体魄和运动基因,埃里森后来成为“美洲杯”帆船赛的参赛者。埃里森出生不久,他的生母意识到无法独自养活这个孩子,就把他送给了自己在芝加哥的姨夫和姨妈抚养。而埃里森直到48岁才再次见到自己的生母。和乔布斯一样,埃里森从养父母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关爱。中学时的埃里森是个聪明但表现并不突出的孩子,这一点也和乔布斯类似。高中毕业后他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 Champaign)和芝加哥大学读书,和乔布斯一样,他也没有完成学业,大学没读几年,22岁就到了硅谷工作。在掌管甲骨文后,埃里森也和掌管苹果的乔布斯一样,不断(通过董事会)给自己大量地发股票。另外,他们对竞争对手都非常“狠”。
……
正是因为埃里森有这种为了办成事情不计成本、志在必得的决心,商业眼光敏锐,执行力非常强,达成了很多在他人看来根本做不到的奇迹。跟盖茨和乔布斯一样,埃里森对竞争对手毫不留情。如果埃里森处在盖茨的位置,他对整个PC行业的垄断会更强。事实上,在过去的30多年里,埃里森领导的甲骨文扫荡了几乎所有独立的数据库系统公司和应用服务公司,除了IBM和微软。而埃里森的手段也非常简单直接:恶性竞争和强行收购。可以肯定地讲,没有埃里森,今天的甲骨文最多是一家规模不大的二流软件公司。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埃里森是如何创造奇迹的。
2 钻了IBM的空子
3 天堂下的帝国
……
应该说,埃里森的确没有从郭士纳和盖茨身上占到便宜。这两个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光芒是如此的闪亮,以至于璀璨的群星都黯然失色。但是,埃里森领导的甲骨文最终还是赢了,因为他熬到了这两个人离开CEO的岗位。这就如同中国晋代的司马懿和日本战国时代的德川家康,当其他巨人(三国时的曹操、刘备和孙权;日本战国时代的丰臣秀吉和武田信玄)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的时候,他们便开始唱主角了。郭士纳的继任者彭明盛(Samuel J. Palmisano)和盖茨的继任者鲍尔默在境界上显然都比埃里森低一个档次。此刻,便到了甲骨文开始追赶IBM和微软的时候了。2005年,甲骨文获得了46.8%的数据库系统市场份额,超过IBM和微软的总和(分别是22.1%和15.6%)。2006年,甲骨文的市场份额继续增加到47.1%,而它的老对手IBM继续下滑到21.1% 2007年,甲骨文继续将市场份额扩大到48.6%。在此之后,虽然受到开源数据库的挑战,甲骨文基本上维持住了48%左右的市场份额,并且一直超过IBM、微软和SAP三家的总和。甲骨文最终的胜出有多种因素,尤其是埃里森个人的能力不容忽视,这一点是其他公司学不来的,但是还有其他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甲骨文胜在定位和产品的推广上。对外一向高调的埃里森不断强调甲骨文是数据库公司,而IBM是一个系统服务公司。也许埃里森说的没有错,IBM可能因为DB2太依赖于自己的主机和服务器,而渐渐丧失了数据库的市场份额。我们在这本书中已经看到,而且还会经常看到,一个产品线较长的公司,在某个产品上往往竞争不过专门从事这项产品的专一公司。比如摩托罗拉在处理器上竞争不过英特尔、在手机上竞争不过诺基亚,苹果和太阳在操作系统上竞争不过微软,微软在在线业务上竞争不过早期的雅虎,更竞争不过后起之秀Google和Facebook,雅虎在搜索上竞争不过Google,而Google在社交网络上竞争不过Facebook。在中国也是类似,百度和腾讯在电子商务上竞争不过阿里巴巴。这里面不仅仅是产品线较长的公司容易“分心”,更重要的是市场和用户对专一的公司更容易认可。大部分专一的公司未必会专门强调竞争对手是个“综合”而非专一的公司。比如,微软从来没有攻击苹果不是专门的“操作系统”公司,Google也没有攻击雅虎和微软不是搜索公司。但是,埃里森却永远把这一点挂在嘴边。在产品推广上,埃里森经常拿自家苹果跟竞争对手的橘子作对比,宣传自家产品的长处,贬低竞争对手的产品。大部分公司在广告中一般只宣传自己的产品好,而不会专门找一个主要竞争对手来贬低,甲骨文却总是反其道而行之。据一位甲骨文的老员工讲,与竞争对手做性能对比测试时,甲骨文往往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并不具有太强的指导意义,但测试结果却会给用户很好的印象。如图8.3所示,是甲骨文比较他们和IBM产品的广告。2010年初,埃里森和IBM一位战略主管伯尼·斯庞(Bernie Spang)在ComputerWorld的主持下进行了一次对话,埃里森一上来就攻击IBM——说IBM比甲骨文落后十年,不能管理大数据,没有云功能,不能在集群服务器上运行,等等IBM这位看来不是很聪明的主管面对埃里森咄咄逼人的不实攻击,不断被动地解释和防守,完全落了下风。
2010年以前,甲骨文最大的硬件合作伙伴是惠普公司,后者为甲骨文提供数据库的服务器。但是,在收购太阳公司,有了自己的服务器(SPARC)之后,甲骨文便通过广告打击惠普公司,除了宣传惠普的服务器性能差外,还打出这样一套非常有攻击性的广告——“把你的惠普服务器扔到垃圾堆,我们给你SPARC服务器打对折!”微软前CEO鲍尔默易然不喜欢苹果的产品,但是也只能在微软公司内部鼓励员工将苹果的iPod换成微软的Zune,而不敢赤裸裸地做这样的广告,但是埃里森却敢。易然业界对这种言行颇有微词,但是对甲骨文来说效果居然不错。

图8.3 甲骨文和IBM对比产品的广告
其次,甲骨文历来重视利润,很少做吃力不讨好的花样文章。商人挣钱本是天经地义,但是近20年来,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怪现象,就是谁烧钱越多,本事越大。2006年,Google为了推广它不成功的支付系统Checkout,给Checkout用户一次消费满50美元补贴20美元,这已经很荒唐了。2011年,中国还有一家公司为了做电子商务,给一次消费满200元人民币的顾客300元的返券,这就让大家不知所云了。事实证明这些钱都是白烧了。埃里森从来不做这种傻事,他给销售人员定的指标历来是以利润为先,而不仅仅是销售额,因为不赚钱的事埃里森从来不做。据甲骨文的员工讲,埃里森非常抠门,平时给员工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就远远不如IBM,遇到宏观经济不好的年代,裁员自不必说,还要削减各种福利。硅谷很多公司先后被评为全美最佳雇主,但这个荣誉与甲骨文公司绝缘。但是正因为注重成本控制,即倬在2001年和2008年两次经济危机中,甲骨文都不仅还能盈利,而目利润率几乎没怎么下降,见表8.1。易然笔者并不很赞同埃里森这些“抠门”的做法,但是他不重花架子、重视利润的做法值得那些不负责任、胡乱烧钱的公司学习。毕竟,公司长期稳定发展是靠自身的利润支持,不是靠政府的政策和投资人的输血。另外,甲骨文长期稳定的盈利事实上保证了广大员工的饭碗。2008一2009年金融危机时,以前那些对员工非常友善的公司,如太阳、思科和雅虎等,因为冗员太多导致利润大幅下滑,就不免大规模裁员,但是甲骨文公司因为利润有保障,员工的饭碗就稳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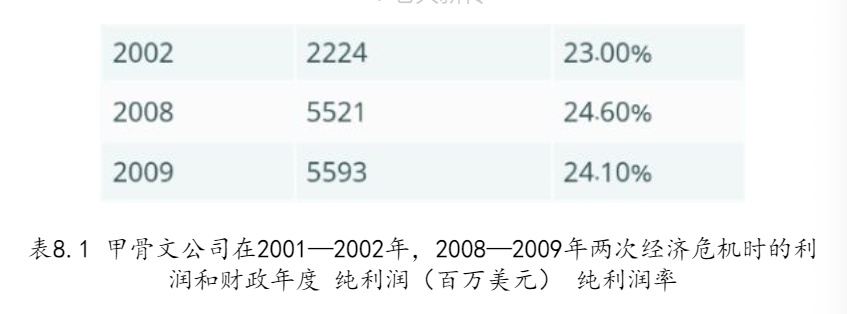
表8.1 甲骨文公司在2001—2002年,2008—2009年两次经济危机时的利润和财政年度 纯利润(百万美元) 纯利润率
最后,甲骨文的成功也离不开很多次成功的并购,同时它具有很好的消化和整合新公司的能力。从产业链的角度看,全球数据库市场可以分为两部分:上游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也即甲骨文、微软和IBM的产品,以及在此基础上为特定用户二次开发的应用系统。在甲骨文以前,IBM等公司同时从事两部分系统的开发。甲骨文和微软发明了卖软件的模式后,数据库公司只关注第一部分(即数据库管理系统),第二部分(即应用系统)基本上由第三方小公司,或者用户自己开发。和所有行业一样,这些针对企业用户做二次开发的公司经过若干年的竞争,逐渐形成了一些比较大的龙头公司,它们控制着部分企业级市场。甲骨文就是通过收购这些公司不断获得数据库市场的份额。其中最著名的是2005年并购企业级应用软件巨头仁科股份有限公司(Peoplesoft)。
仁科由大卫·杜菲尔德(David Duffield)于1987年创立。杜菲尔德长期和IBM合作,企业级软件的研发和市场经验非常丰富。自成立起,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仁科成为全球第二大(独立的)企业级应用软件公司,并且主导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软件的市场。杜菲尔德和埃里森个人是老对头,他对甲骨文的产品也不感冒。因此,两家公司的合作看上去是完全不可能的。为了抢占这块市场,埃里森决定强行收购这家公司。从2003年起甲骨文多次提出要收购仁科。杜菲尔德本人根本不想卖公司,他的公司经营得很好,没有必要和甲骨文合并,但是他不能完全控制董事会。2004年因为价格的分歧,仁科的董事会拒绝了埃里森的并购提议。同时,美国和欧盟司法部以可能造成垄断为由,也驳回了甲骨文的请求。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讲,埃里森认准了的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一方面提高了收购价格,这回仁科大部分董事同意了,杜菲尔德也无力回天。同时,埃里森承诺保留仁科90%以上的员工,美国和欧盟也不必为失业担心了。经过长达两年的努力,这桩价值103亿美元的并购终于达成。甲骨文从此垄断了人力资源管理软件市场。
接下来几年,甲骨文每年都有一次大的并购。2006年,它花了58.5亿美元收购了Siebel公司;2007年,用33亿美元收购了Hyperion公司;2008年,以85亿美元收购BEA公司。这些公司都是在企业级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的软件和服务公司。在收购这些公司后,甲骨文将它们原来的用户转换成自己数据库的用户,一度获得了全球超过一半的数据库系统市场份额,一个企业级软件帝国就此形成了。埃里森虽然给员工的待遇一般,却从不亏待自己。他的办公室在甲骨文红木滩(Redwood Shores)总部几栋数据库形状(圆柱形)大楼中最高一栋的最高几层——这是甲骨文公司离“天堂”最近的办公室。甲骨文公司的员工说,公司的层级比较分明,而埃里森在天堂级。他每天从“天堂”上俯视自己的帝国。
如果只满足于做世界上最大的企业级软件公司,那么埃里森就不是埃里森了。长久以来,埃里森一直梦想能全面挑战IBM,成为全球企业级公司的龙头。但是,这件事在过去非常困难,因为甲骨文自己没有服务器和操作系统,很难同步优化硬件系统和数据库。2009年,埃里森的机会来了,因为金融危机,过去服务器行业的龙头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快要支撑不住了,四处寻求并购的伙伴。IBM因为业务和太阳公司有较多重叠,很难通过反垄断的审核,失去了收购太阳公司的机会,甲骨文成了唯一可能的收购者。易然美国政府和欧盟对这桩收购案都有所保留,并目不断阻止这次并购,欧盟还为此和甲骨文打官司,以至于太阳公司的不少人都怀疑并购最终能否被通过。但是,了解埃里森的人都知道埃里森从来不怕打官司。果然,埃里森再次倬出他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劲头,和欧盟死磕。而太阳公司的员工已经做好了被收购的准备,在这期间毫无工作的动力,导致公司业绩不断下滑,进而导致它在欧盟国家不断裁员。最终,迫于失业的压力,欧盟不得不向甲骨文低头了。2010年,这桩价值74亿美元的收购得以达成。
花钱收购公司非常容易,几乎每一个有现金的公司都能做到,但是能将收购来的公司整合好却是一多半公司做不到的。微软从2000年以后,也收购了不少公司,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些公司对微软的业务有什么帮助。IBM收购了很多被微软打败的公司,比如莲花公司和Informix公司等,但是也没有看到它们对IBM的长期业绩有太多帮助。而埃里森对收购来的公司的负责人,通常是毫不留情地要求他们走人,并送上一番冷嘲热讽。对下面的员工,则要求迅速融入甲骨文的文化。在这么多的并购中,我们可以通过甲骨文对太阳公司的整合一睹埃里森和他的公司在这方面的艺术。
太阳公司在被并购前产品线颇长,从SPARC处理器到服务器、工作站,再到操作系统Solaris(UNIX的变种),免费的Java语言和工具。后来因为硬件利润率低,Solaris的市场份额下滑,太阳公司在最后几年里又收购了一家做存储的公司,试图进入云计算领域。另外还收购了开源数据库MySQL,试图进人IT服务业与IBM、惠普和甲骨文竞争。简而言之,太阳公司产品多但竞争力差,业务方向不明确,常年亏损。在被甲骨文收购前,太阳公司还有三万多员工,但是人员相对老化。外界对甲骨文能否整合好太阳公司深表怀疑,如果整合不好,甲骨文也会被拖垮。但是埃里森却信心十足,他认为自己捡到了大便宜。他提出了以前太阳公司董事会想都不敢想的目标,一年时间让太阳公司盈利10亿美元。
整合主要集中在产品和人员两方面。在产品方面,太阳公司的产品线很长,而几乎每个产品都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
SPARC处理器。该处理器速度曾比英特尔x86系列处理器更快,但是现在速度更慢,价格却更高。后来正是因为如此,太阳公司自己都没有信心继续做下去,而是开始同时制造英特尔x86的服务器。
SPARC的工作站和服务器,价格比同性能的Linux服务器贵一倍,不过优点是可靠性高。世界上各个公司的硬件子公司或者部门基本上是不挣钱的,尤其是2000年后,基于英特尔x86处理器和Linux操作系统的廉价服务器将这个行业的利润率压得极低。
操作系统Solaris,比Linux安全可靠,但是Linux借着开源和免费,抢占了Solaris的大量市场份额。最后逼得太阳公司也搞开源Solaris。
Java,在业界倬用广泛,但它是免费的,耗掉了大量人力,太阳公司却一直没有找到挣钱的办法。
收购的开源数据库MySQL,易然对太阳公司有用,但对甲骨文是鸡肋。
收购的存储设备公司,太阳公司没有整合好,也成了鸡肋。
外界猜测埃里森的融人计划应该是:剥离SPARC处理器和服务器等硬件业务,将它们卖给富士通公司(Fujitsu),因为后者一直在为太阳公司做OEM的产品。Solaris和Java要保留,但是大家猜测埃里森如何收费。至于MySQL,对甲骨文而言没什么价值。
2010年的一天,并购完成后,太阳公司的高管们按照埃里森的要求做好了产品策略报告,第一次向埃里森汇报。那天不知什么原因,埃里森到得稍微晚些,太阳公司的高管们在会议室里等待。过了一会儿,一个秘书来通知“埃里森已经离开了办公室往这边过来,请大家做好准备”。几分钟后,秘书又来通知“埃里森已经接近电梯,请大家做好准备”。又过了几分钟,秘书再次来通知“埃里森已经出了电梯,正朝办公室走来,请大家做好准备”。这时,埃里森已经到了会议室。太阳公司的高管们开始按照精心准备的投影胶片介绍自己的想法,但是,还没有讲几分钟,埃里森就打断汇报,直接到白板上连比划带讲,说我们要这么这么做,然后会议结束。至于埃里森讲的是怎么做,我没有参加会议,自然编不出来,但是从埃里森后来的做法能看出他的思路。
首先,埃里森要突出太阳公司SPARC服务器和廉价Linux服务器的差别,就如同奔驰车和丰田车作为代步工具易然差别不大,但是毕竟不属同一档次,要在不同市场出售。埃里森将SPARC服务器和甲骨文的数据库捆绑,去和IBM的设备竞争(较贵)。甲骨文将数据库和太阳公司的硬件系统结合再优化,整体性能比IBM同类产品提高了几倍(至少广告上是这么宣传的),然后甲骨文抛弃了原先的硬件合作商惠普公司,和惠普全面开战,争夺服务器市场的份额。仗着全面优化的性能,甲骨文在2010年、2011年两年继续蚕食IBM数据库的市场,并目最终把后者变成了远远落后的行业第二名。于是,原本看似鸡肋的产品,到了埃里森手上就玩活了。
其次,对于已经开源的Solaris操作系统,埃里森不再支持,新版本的操作系统不再开源,因为埃里森从来不做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对于大家认为毫无用处的MySQL,埃里森倒是找到了一个死马当作活马卖的办法,用来和Google打官司,因为Google不仅是MySQL最大的用户,而且旗下Android应用平台(Application Framework)用的是Java,却没有付过钱。甲骨文和Google的官司涉及很多知识产权(包括版权、技术和专利等)的侵权问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易然法官一度认定是Google侵犯了甲骨文的版权,但是甲骨文的专利中很多是公众知识(Public Domain Knowledge)而非特有的技术,因此最终法庭判定Google无须支付专利赔偿金,只需支付少得可怜(且远远低于甲骨文的律师费)版权费。后来Google不依不饶连几万美元的版权费都认为不该付,双方从上诉法庭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终2015年最高法院认可了甲骨文在Java上的版权。虽然这个结果从经济上看是两败俱伤,因为双方付出了高昂的律师费,但是甲骨文至少赢了面子。这件事充分反映了埃里森的做事风格,能打的官司一定要打。而另一家与甲骨文打官司的SAP公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经过几年马拉松式的官司,2012年SAP同意向甲骨文支付高达三亿美元的赔偿金,虽然前者认为对后者造成的损失只有几千万。
整合太阳公司业务最后的一步,也是最艰难的一步,就是人员的整合。甲骨文首先一次性地裁掉了一批人,但也是最后一次裁员,留下的人都安心了。太阳公司里有很多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兵,职级都不低,但是在太阳公司已经懒散惯了,被收购后,都得按时定量地完成工作,虽然心里不痛快,时间长了居然也就习惯了。用一个字来形容埃里森,就是一个“狠”字。就这样,甲骨文成功地消化了太阳公司的业务和近三万名员工。
甲骨文这种务实而严格的管理方式也有它的弊端,就是很难造就有创新的人才。在富于创新的硅谷,从甲骨文出来创业成功的人并不多,这多少说明一些问题。再有,甲骨文这样的管理风格在IT领域能够执行下去,多少靠埃里森个人的能力,一旦埃里森退休,这种管理风格是否可行,也令人怀疑。
甲骨文公司的发展可以用平淡无奇来形容,它更多是靠着很好的管理和经验一步步做起来的。它的第四条成功经验就是很少犯错误。我们在这本书中不断总结各个公司所犯的错误,甚至微软和苹果也不例外,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我们很难找到甲骨文明显的错误。正如巴菲特在讲解投资的秘诀时强调,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做对了多少件事,而在于少犯多少错误。自上个世纪70年代创立开始,几十年间甲骨文几乎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这在IT领域非常少见。
2011年,甲骨文公司的营业额达到356亿美元,税后利润也达到创纪录的85亿美元,不仅是全球企业级市场上遥遥领先的第一名,增长速度也比微软快。2007一2011年,甲骨文的营业额增长了98%,而微软只增长了36%。在纯利润方面,前者正好翻了一番,而后者只提高了64%(易然也很好了)。甲骨文业务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并购。但是在随后的几年里,它因为很难再找到可以并购的大公司,增长明显放缓,到2018年营收只达到400亿美元左右,7年间只增加了12%。不过,甲骨文向基于云计算和SaaS的新业务转型,因此利润上升得比营业额要快很多,达到了132亿美元,同期增加了55%,这在老一代IT企业中表现算是不错的。在可预见的未来,甲骨文依然要跟老对手IBM、微软、SAP竞争,而且还要面对新对手Salesforce和惠普等企业的挑战。
2014年,埃里森在IT行业打拼了近半个世纪后,终于退出了IT的第一线,而与他同时代的郭士纳、盖茨等人则更早就离开了IT行业。接替埃里森的是曾将惠普扭亏为盈的前CEO赫德和甲骨文过去的COO卡茨(Safra Catz),两人被任命为共同CEO。在新的时代,赫德和卡茨或将有新的作为,但是甲骨文作为一个并购机器的基因已由埃里森塑造完成,在未来并购恐怕依然是甲骨文拓展新业务和向云计算转型的主要手段。
结束语
甲骨文的兴起,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它最早看到关系型数据库的市场前景,并目在商业模式上优于IBM。甲骨文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传奇,而是靠相对平稳但可持续的发展,它的故事也许是这本书中最枯燥的。甲骨文公司幸运地处在了计算机行业软硬件分工的年代,并把握潮流,真正促成软硬件产业的分工。甲骨文提供了全球使用率最高的数据库管理系统,而更大的贡献在于它证明了软件公司不仅可以靠卖软件的使用权而独立于硬件公司存在,并目可以比硬件公司活得更好。甲骨文的成功,也再次说明了创始人和领袖的重要性,可以说没有埃里森,就没有甲骨文今天的辉煌。
甲骨文公司大事记
1977 埃里森等人创立了甲骨文公司的前身软件开发实验室。
1978 基于关系型数据库的系统Oracle 1诞生。
1979 Oracle 2诞生,公司改名为关系软件公司。
1981 古普塔加盟该公司,并目为公司写了第一份商业计划书,明确了公司今后开发通用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和开发工具的发展方向。
1982 关系软件公司正式改名为甲骨文公司。
1984 红杉资本注资甲骨文公司。
1986 甲骨文公司上市,当年营收为5500万美元。
1989 甲骨文公司将总部搬到加州硅谷地区的红木滩市。
1994 甲骨文收购DEC数据库部门RDB,并目开始了它长期大规模并购的历史。
1995—1996 埃里森提出网络PC的概念,甲骨文发布自己的浏览器,易然这些产品不很成功,但是被认为是云计算概念的前身。
2000 甲骨文和IBM,微软在数据库市场上基本上三足鼎立。但此后,甲骨文发展速度远高于对手。
2004 甲骨文以103亿美元的高价强行收购了仁科股份有限公司。
2005 甲骨文在数据库市场的份额首次超过IBM和微软的总和。同年,甲骨文以58亿美元的高价收购Siebel系统公司。
2008 甲骨文以72亿美元的高价收购BEA系统公司。
2010 甲骨文在数据库系统市场的份额首次超过50%,同年完成对太阳公司的并购,并以太阳公司的专利开始状告Google专利侵权,诉求高达61亿美元的损失补偿。但是此案最后被判不成立,除了律师费外,甲骨文还掏了一百多万美元的诉讼费。
2011 甲骨文开始大量收购基于云计算的企业级软件和服务公司,并高调进入云计算领域。
2014 埃里森辞去CEO一职,将甲骨文交给了赫德和卡茨。
第9章 互联网的金门大桥 思科公司
1 好风凭借力
2 CEO的作用
在思科的发展过程中,钱伯斯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两个创始人波萨卡和勒纳。在互联网开始腾飞、数据通信呈指数增长的年代,如果没有波萨卡和勒纳发明路由器,也会有别人发明,因为社会需要这样一种通信设备。但是,如果没有钱伯斯,全世界数据通信设备产业的格局就可能有所不同,而目可以肯定思科不会成为今天这样一家全球性的跨国公司。早年给思科投资的红杉资本创始人瓦伦丁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在思科公司上市后果断换将,支持钱伯斯接替两位创始人,当上了思科的第一把手。在1995年初钱伯斯接手思科时,它还只是一个拥有4000名员工,营业额不到20亿美元的中型企业,而在2015年钱伯斯离任时,思科已经成为了在全球拥有7万多名员工,年收入近500亿美元的超大型跨国公司。因此,谈到思科就不能不说说钱伯斯,这就如同谈GE必须说韦尔奇,谈IBM必要讲郭士纳一样。透过钱伯斯在思科发展过程中的贡献,我们也能看出一个好的CEO对于一家公司是多么的重要。
钱伯斯1944年出生于美国东部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不过他从来没有获得过名校的学位,这可能和他在年轻时有阅读障碍症有关。直到今天,钱伯斯依然喜欢口头交流而不是读长篇汇报。钱伯斯并不是学计算机出生的,但是他先后在IBM和王安电脑公司工作过。在这两家公司,钱伯斯学会了如何尊重客户,并且业绩越做越好,一直做到王安电脑的北美区总裁。1991年,由于钱伯斯不愿意裁撤北美总部的4000名雇员,干脆辞去王安电脑的工作,这时思科公司看中了他,聘请他为主管全球销售和运营的高级副总裁。4年后,钱伯斯升任思科公司的CEO。
钱伯斯虽然不是技术出身,但是在商业上目光敏锐。不过即便如此,钱伯斯也很少我行我素,强制推行他的想法,他总是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既有来自下属的,也有来自客户的。接触过钱伯斯的人讲,他从来不训斥下属,而且从来不是一个顶层设计者。钱伯斯总结IBM的失误之处和王安电脑失败的教训后认为,这两家公司的问题都不是出在技术上,而是出在企业文化上。IBM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连续十几年走下坡路是因为远离了客户,而王安电脑公司的问题在于内部糟糕的家族式管理。因此,钱伯斯在接管思科后,首先着眼于建设一种健康的企业文化,而这种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善待员工。
思科公司把40%的雇员期权分给了普通员工,这么高的比例在美国的公司里是绝无仅有的。今天,Google等以善待员工著称的公司都做不到将这么多的期权分给普通员工。钱伯斯对待员工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刺激,而是出于真正以人为本办企业的原则。思科的一位老员工曾经这样回忆钱伯斯对她工作的支持:1998年,钱伯斯要提拔她升任主管人事的副总裁,但是她感觉无力胜任,因为家里有三个孩子要照顾。钱伯斯表示,如果思科不能帮助她解决后顾之忧,那么也就算不得是一个明星公司了。钱伯斯曾经这样谈论他对一个成功企业的看法:“最有影响力的公司不仅实力最强大,而且也最为慷慨大度,富于人情味和诚意。成功的企业不仅能够吸引而目也能够留住天才员工。”在钱伯斯人性化的管理下,即倬是在2000年大公司员工跑到小公司创业成为风尚时,思科的员工流失率依然非常低,很多员工甚至懒得接猎头们的电话。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就明白为什么钱伯斯在2000年裁员时是那么的不情愿,他并非演戏,而是打心眼里觉得对不起那些被裁掉的员工。
钱伯斯在管理上的第二个秘诀就是无条件地满足客户的需求。钱伯斯本人不是技术出身,对技术的把控来自于两个方面:下属的建议和客户的需求。和钱伯斯打过交道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位难得的沟通大师,并且非常有耐心听取客户的意见。在钱伯斯手上,思科由一个主营路由器的公司,变成了有几十条产品线的网络通信设备公司,以满足很多客户对一站式解决方案的需求。钱伯斯对各个产品的要求是要做到全球前两名,如果做不到,要么和世界前两名合作,要么干脆并购那个细分领域中的老大。关于思科的并购策略,我们会在下面一节中详细介绍。
钱伯斯被认为是信息时代的管理大师,他的很多做法被IT公司普遍采用,比如将工业时代的层级森严(Rigid Hierarchy)树状组织结构,变成网状(Network)结构,这样至少会在公司内带来三个好处:
上下级和不同部门之间沟通的路径较短;
部门壁垒低,便于合作;
组织架构灵活,便于随时终止市场前景不好的旧项目和开展有潜力的新项目。
关于树状和网状这两种企业结构的特点和差异,我们会在后面介绍。总之,进人后信息时代以后,管理的灵活性是企业活力的保障,而钱伯斯在这方面的尝试后来也成为商学院的经典案例。
从1995年一直到2000年,思科在钱伯斯的领导下,无论是在产品研发还是在营销上,一直保持着惊人的发展速度。虽然每个季度华尔街都会略微调高一点对思科盈利的预期,但是思科居然做到了在连续十几个季度里均超出华尔街的预期。从诞生到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微软用了25年,而思科只用了16年。可以说,没有钱伯斯,就没有思科的高速发展。
至于在公司成长大了之后,如何保持公司的创造力,钱伯斯更有他与众不同的、让公司能够持续发展的绝招。
3 持续发展的绝招
思科上市后,两个创始人马上成了亿万富翁。思科今天(2019年2月6日)的股价,是上市时的700倍左右。思科的早期员工,只要在理财上不是太冒险,比如在互联网泡沫时代没买很多网络垃圾股(当时叫网络概念股),就也成了千万或百万富翁。这些人在成为富翁之后很多会选择离开公司去创业,或者干脆退休。事实上,思科的两个创始人就选择了这条路,离开了公司。
一家成功企业的早期员工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他们一般是一些非常爱冒险的人,否则就不会选择加人新开办的、甚至是还没拉到投资的小公司,他们的技术和能力非常强,常常可以独当一面,因为早期的公司要求员工什么都得能干。同时,他们对新技术非常敏感,否则就不可能在众多新兴公司里挑中那些日后成功的公司。但是,这样的人也有弱点。他们易然善于开创,但不善于或不愿意守成,而守成对于大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他们做事快,但不够精细,因为在公司很小时,抢时间比什么都重要。一般在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他们会和新的管理层发生冲突——新的主管会觉得他们不好管。这就如同打江山的人未必能治理江山,这些员工很可能自己出去开公司。而即使留在公司,这些早期员工都已腰缠万贯,原先的动力也大打折扣。因此,如何留住早期员工,并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便成了每一个上市科技公司的难题。
另外,一家公司大到一定程度后,每个人的贡献就不容易体现出来,大锅饭现象几乎是全世界的通病。一些员工即使有很好的想法,也懒得费工夫去推动它,因为自己多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最多能多得百分之几的奖金。偶尔出来一两个人试图推动一下,又会发现在大公司里阻力很大。因此,有些员工一旦有了好的想法,宁可自己出去创业,也不愿贡献给所在的公司。这两个问题在硅谷普遍存在,而思科则是将这些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公司。
思科的办法很像大航海时代西班牙国王和葡萄牙国王对待探险者的做法。那时,包括哥伦布和麦哲伦在内的很多航海家都得到了王室的资助。这些冒险者很多是亡命之徒,其航海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名垂青史,而是为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他们和王室达成协议,一旦发现新的岛屿和陆地,则以西班牙或葡萄牙王室的名义宣布这些土地归国王所有,同时国王封这些发现者为那个岛屿或土地的总督,并授予他们征税的权力。这样一来,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国的疆土就得以扩大。
为了让思科能够不断发展新业务,思科的CEO钱伯斯采用了一种宽容内部创业的政策。具体的做法是,如果公司里有人愿意自己创业,公司又看好他们做的东西,就让他们留在公司内部创业而不要到外面去折腾,而思科会作为投资者而不再是管理者来对待这些创业者。一旦这些小公司成功了,思科有权优先收购,思科的地盘就得到扩大。而这些独立的小公司的创办者和员工,又可以得到很高的回报。这样本来想离开思科出去创业的人也就不用麻烦了,接着上自己的班,只是名义上换了一家公司。当然,如果这些小公司没办好关门了,那么思科除了赔上一些风险投资,也没有额外的负担。这种做法不仅调动了各种员工,尤其是早期员工的积极性,也避免这些员工将来成为竞争对手,或者加人对手的阵营。思科的这种做法后来被Google学到了。今天Google的X-labs等带有内部孵化性质的部门,就是学习思科管理方法的产物。
思科自己公布的从1993年起的收购超过百起,这还没有包括很多小的收购。以1999年思科以70亿美元的天价收购Cerent公司为例,后者本身就是由思科前副总裁巴德尔(Ajaib Bhadare)创办的,从事互联网数据传输设备制造,并目在早期得到思科1300万美元的投资。Cerent的技术和产品显然是思科想要的。事实上,从思科分出来的这些小公司比其他的创业公司更容易被思科收购。因为,一方面这些创始人最清楚思科想要什么技术和产品,也最了解思科本身的产品,以便为思科量身定做。另一方面,他们容易得到风险投资的支持,因为风投公司能看得到它们投的公司将来的出路在哪里一一卖回给思科。所以,在硅谷一些想通过新兴公司上市或出售发财的人,当看不准哪个公司有发财相时,简单的办法就是加入那些思科人,尤其是思科高管和技术骨干开的小公司。这一招在千禧年的前几年颇为灵验,当然这些弄潮儿也得有真本领,能让人家看得上。
在思科,人们经常会遇见自己“二进宫”甚或“三进宫”的同事。一个员工因为转到思科支持的小公司,从名义上讲暂时不算思科员工了,但是随着思科收购那家小公司,这位员工再次“加人”思科。他出去转了几年,回到原来的位置,却已腰缠万贯。
当然,思科的这种做法在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同时,也保证了它能不断获得最新的技术,提高竞争的技术门槛,从而将低端竞争对手挡在市场之外。如果说微软是赤裸裸地直接垄断市场,那么思科则是通过技术间接垄断了互联网设备的市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硬件制造商的利润不会太高(20%左右),但是思科却能在很长的时间里做到高达65%的毛利率,不仅在整个IT领域大公司里排第二位(仅次于微软80%的毛利率),而且远远高于一般人想象的高利润的石油工业(35%)。这几年,由于受到华为的冲击,思科的毛利率有所下降,但依然能维持在60%的高水平,这简直是一个奇迹。(相比之下,华为的毛利率只有40%左右。)这种高利润只有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司才能获得。
思科这种鼓励一定程度的叛逆的做法,既有它宽容和大度的一面,这来自于它的基因,同时也是因为它对自己的产品和市场有信心。
思科自身的创建就是用到了两个创始人的职务发明。斯坦福大学当时易然很想独占“多协议路由器”的发明,但是最终还是很开明地和两个发明人共享了这项技术,支持他们夫妻二人拿了职务发明创办公司,斯坦福大学自己换得一些思科的股票。思科上市后,波萨卡和勒纳向斯坦福捐了很多钱,他们和斯坦福通过思科实现了双赢。波萨卡和勒纳把这种对叛逆的宽容基因带到了公司,而后来的钱伯斯也是一位具有胸怀和远见卓识的CEO,他将这种做法变成了思科的传统。当然,思科能做到宽容员工用自己的职务发明开办公司,也是因为思科员工的发明,一般很难单独成为一种产品,而必须应用到现有网络通信系统或设备中,因此它们最好的出路就是卖给思科。所以,思科倒是不怕这些小公司将来翻了天。不仅思科如此,华为一些离职的高管,从过去的CTO李一男到海思早期的负责人,均离职创业,试图和前东家竞争,却都无法成功,原因也相似。
托尔斯泰讲,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信息产业中,这句话要反过来说,成功的公司各有各的绝招,失败的公司倒是有不少共同之处。思科这种成功的做法,一般的公司是抄不来的。
4 竞争者
5 诺威格定律的宿命
Google研究院前院长、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彼得·诺威格博士说,当一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以后,就不要再指望在市场占有率上翻番了。这句话在信息产业界广为流传,道理也很简单,但是常常被一些公司领导者忽视。在互联网泡沫时代,太阳公司占据了绝大部分工作站市场,市值一度超过一千亿美元。但是,它还在盲目扩大,试图在工作站和服务器上进一步开拓市场,结果,一旦经济进人低谷,工作站和服务器市场迅速收缩,即倬它占到100%的市场份额也无济于事。事实上,太阳公司的市值在互联网泡沫破碎后,一下就蒸发了90%多。
思科公司从2003年美国走出因互联网泡沫导致的经济危机后,就一直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在很长的时间里,它占据了世界网络设备市场的一大半,即倬它把全球市场都占掉,也很难使公司再成长一倍。今天,思科和华为两家平分了全球市场。由于反摩尔定律的作用,这两家企业即便能多卖了一些设备,收入也不会成比例地提升,因为价格在不断下降。因此,除非它们能开拓出新的市场,否则会成为下一个朗讯或北方电讯(简称北电)。要摆脱诺威格定律的宿命,就必须找到和原有市场等规模,甚至是更大规模的新市场。如果仅仅找到一个很小的新兴市场,是远远不够的。
思科的舵手钱伯斯很早就未雨绸缪了。思科是最早大力投入VoIP(Voice over IP),即用互联网打电话业务的公司,它收购了这个领域颇有名气的Linksys公司,并目通过VoIP电话进入了固定电话设备市场。思科还为这种基于IP的电话注册了Iphone商标(大写的I,小写的p),并目是在苹果之前。因此,苹果出了iPhone后,在名称上和思科的产生了冲突和法律纠纷。最终,苹果从思科手里买下了iPhone的名称,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今天,美国的大部分电话公司,包括AT&T和Verizon都提供这种倬用网线的电话服务。而在国内,包括腾讯在内的无数公司,内部用的都是思科的VoIP电话。同时,思科进军存储设备和服务业务,也收购了一些相应的公司,为它的VoIP战略做策应。随着基于互联网的VoIP电话的普及,网络路由器代替了原来程控交换机的地位,思科也代替了朗讯的地位。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讲,不断缩小的语音通话市场远不足以让思科维持一个体面的增长。
在钱伯斯担任CEO的时代,他能够看到的就是利用互联网更多地取代过去各种网络所提供的业务,包括利用在线视频取代电视,利用云存储取代企业和个人的本地存储,等等。最终各种和工作、生活和娱乐相关的通信都将通过互联网合并到一处,而思科将为所有这些通信提供网络设备和存储设备。2007年我在写本书第一版时描绘了一种家庭通过X over IP使用电话、电视和互联网的场景,这里面X可以包含任何东西。当时我不确定的是设备制造商、运营商和内容提供商谁将最终获利,十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是运营商和Google、Netflix等提供内容服务的公司获利更多,而网络设备公司得到的实惠可以忽略不计。
相比思科,华为则幸运得多,魄力也大得多。华为的幸运之处在于,当它遇到诺威格宿命的瓶颈时,移动互联网正在快速兴起,而它的魄力则体现为居然敢于跨行业进军智能手机的市场。易然在非IT人士看来,制造路由器等网络设备和制造手机都属于IT领域,应该相差不大,但是它们其实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制造网络和通信设备,针对的是运营商的市场,工程师们就是按照通信协议做事情,可以说是有章可循,其核心竞争力在于谁做得快,谁的性能好,价格还够便宜。智能手机则属于互联网特征很强的消费电子产品,如果用户体验不好,性能再好,功能再多,价格再便宜,也未必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华为的很多高管和我说起他们当初的困境一一按照做通信产品的思路做IT产品,做出来的东西完全没有人要,而从IT行业直接招来大量的工程师,又发现他们的工作习惯,甚至工作时间,都和做通信产品的工程师完全不同。华为最终经历了几年的阵痛,解决了这些问题,终于制造出可以比肩苹果和三星的智能手机,并目让手机成为公司主要的成长点。
对比华为和思科这两年的发展可以看出,华为已经走出了诺威格的宿命,而思科反倒还在探索之中。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思科走了类似IBM的发展道路,即不断淘汰利润不高的低端产品,将市场主动让给华为等“中国制造”的公司,并目保守地开拓新领域的成长点,这让它得以守住网络设备市场的半壁江山,没有成为另一个朗讯。不过,从思科近几年的表现来看,它将来会逐渐被华为拉开距离。
结束语
思科无疑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见证者。它对于互联网的重要性相当于AT&T对于电话的重要性:因为它为互联网提供了最重要的设备一—路由器。所不同的是,AT&T经过一百年才达到顶点,而思科走完类似的历程只经历了二十年。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二战之后,科技的发展呈加速态势。然而发展得太快的副作用是,思科也因此过早地进人了平稳而缓慢的发展期。
为了防止自身患上不思进取的大公司病,思科采用了内部创业的独特方法,并屡获成功。但是,这依然无法让思科摆脱中国制造的阴影,同时由于没能像华为那样找到市场规模不小于现有业务的成长点,它在全世界网络设备市场的影响力在不断萎缩。可以说,属于思科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反观它的竞争对手中国的华为,不仅在通信领域不断获得成功,而目及时地通过进入智能手机领域,避免陷人增长的困境。华为不仅成为了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IT公司,也成为了中国制造品质的象征。
思科大事记
1984 思科公司成立。
1986 思科推出第一款多协议路由器产品。
1990 思科公司上市。
1995 钱伯斯担任思科CEO,开创了思科王国。
2000 思科发展达到高潮,垄断了多协议路由器的世界市场;当年思科市值一度超过微软成为全球价值最高的公司,思科股票一天的交易额一度超过整个沪深股市。
2001 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裂,思科业绩急速下滑,股价下跌80%以上,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裁员。
2003 思科在VoIP等领域快速发展,公司重回上升轨迹,但是开始受到来自华为的挑战。
2011 由于思科业绩长期停滞,外界要求钱伯斯辞职的声音越来越高。同年,思科开始大规模裁员。
2015 开创思科王国的一代传奇CEO钱伯斯宣布辞去CEO的位置。同年,华为在销售额上超过思科,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公司。
第10章 英名不朽 杨致远、费罗和雅虎公司
一百年后,如果人们只记得两个对互联网贡献最大的人,那么这两个人很可能是杨致远(Jerry Yang)和戴维·费罗(David Filo),而不是今天名气更大的互联网企业家佩奇、布林、扎克伯格或马云。他们对世界的贡献远不止是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门户网站雅虎公司,更重要的是制定下了互联网这个行业全世界至今遵守的游戏规则一一开放、免费和盈利,并目发明了一种让用户和客户可以不是同一人的新型商业模式。正是因为他们的贡献,我们得以从互联网上免费得到各种信息,并通过互联网传递信息,分享信息,我们的生活因此得以改变。易然今天雅虎已经不再是一家独立运营的公司了,但是人们会把他们俩和爱迪生、贝尔及福特相提并论。
1 当世福特
为什么雅虎能够把互联网办成开放和免费的呢?因为它的创始人杨致远和费罗一开始搞互联网就不是为了营利,而美国在线进军互联网时明确表明要挣钱。作为斯坦福大学电机工程系博士生的杨致远和费罗本来不是学习网络的,但他们和另一个同学搞起雅虎完全是出于对互联网非比寻常的兴趣。1994年,3个人趁教授去学术休假一年的机会,悄悄放下手上的研究工作,开始为互联网做一个分类整理和查询网站的软件,这就是后来雅虎的技术基础。这个工具放在斯坦福大学校园网上免费使用,互联网用户发现通过雅虎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网站或有用的信息。这样,大家上网时会先访问雅虎,再从雅虎进人别的网站。门户网站的概念从此就诞生了,雅虎的流量像火箭一样上窜。网景公司发现这个现象以后,便来找雅虎合作,网景公司在自己的浏览器上加了一个连到雅虎的图标,这样,雅虎的流量增长得就更快了。很快,斯坦福大学的服务器和网络就处理不了日益增长的流量了。只好请杨致远和费罗等人把雅虎搬走,这时,网景公司送了雅虎一台服务器,雅虎公司就正式成立了,这是1995年的事。另外说句题外话,当时和杨致远、费罗一起做雅虎的第三人,这时拿不定主意,也许是他觉得他们三个人趁老板不在私自搞起雅虎已经有点不太合适,再退学去办公司就更不合适了,于是选择了留在学校。如果将世界上最郁闷的人排个队,他一定名列前茅。正如我们在前言中所说,一个人一辈子赶上一次大潮就足以告慰平生了,但是他却在机会面前失之交臂。
有了独立的公司,经费就成了一个问题。杨致远找到了红杉资本,就是投资思科的那家风险投资公司,并成功融资200万美元。几年后,红杉资本又成功地投资Google。和美国在线不同,雅虎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它在网络泡沫破碎以前,甚至在美国主要的都市提供免费的拨号上网服务。雅虎为全球用户提供免费的电子邮件服务,虽然它后来的CEO塞缪尔曾经试图对邮箱收费,但是因为雅虎的用户已经习惯了免费,这件事只好作罢。同样,雅虎的搜索引擎(采用Inktomi的技术)和网站目录向全世界开放,无条件地为全世界的网页建立索引。而此时,美国在线却采用了电话公司注册索引词的方式来查找公司。(有些读者也许并不熟悉美国的电话号码注册方法,即一个公司为了方便消费者记住自己的电话,常常用公司的名称做电话号码,比如AT&T的服务电话是1-800-CALL-ATT,用户可以通过电话键盘上的字母对应出数字,即1-800-2255-288。一个公司要取得这个与公司名相同的号码,必须向电话公司购买。)过去倬用美国在线的用户不仅必须记住公司的网址,还得记住它们在美国在线的注册词,直到美国在线2002年采用Google的搜索引擎为止。如果我们将互联网产业和个人电脑产业做一个对比,那么美国在线相当于封闭的苹果,而雅虎相当于微软,电话公司则相当于个人电脑硬件厂商。美国在线同时扮演个人电脑制造商和操作系统制造商两个角色,因为在它看来,门户网站要挣钱就必须收取上网费,如同软件必须通过硬件挣钱一样。而雅虎只是把互联网的门户做好,上网费交给电话和宽带公司去挣。在Google成为主流搜索引擎以前的很长时间里,大量的用户通过雅虎这个门户访问互联网,门户网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操作系统的作用。事实证明雅虎是对的,由于反摩尔定律的作用和竞争的影响,上网费这笔钱是越挣越少,就如同个人电脑厂商的利润越来越薄一样,而门户网站(后来过渡到搜索引擎)的钱却越挣越多。
采用这种开放和免费的商业模式,雅虎的流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两百万美元很快就花完了。雅虎再次从日本最大的风险投资机构软银(SoftBank)融资,软银开始只占了雅虎股份的5%,但在雅虎快上市时,发现这家公司前途无量,强行将股份占到了近30% ,并且在雅虎上市后,它没有抛售而是增持雅虎的股票,一度占了雅虎近40%的股份,成为雅虎第一大股东。顺便提一句,软银也是中国阿里巴巴公司的投资人,并且一度占了该公司75%的股份,至今仍是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1996年,成立仅一年的雅虎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当天股价从13美元暴涨到33美元。各大媒体争先报道了雅虎上市的盛况,雅虎一下成了互联网的第一品牌,而杨致远和费罗也双双进人亿万富翁的行列。
雅虎的做法为全球互联网公司树立了榜样。Excite、Lycos和Infoseek等公司纷纷效仿雅虎的做法,一年中,各种门户网站相继出现,两年后,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搜狐、新浪和网易也成立了。而同时,采用美国在线商业模式的东方网景开始亏损并被出售。1994—2000年,可以说是互联网的大航海时代。各类网站相继出现,从政府部门、学校、公司到个人都在自建网站,原来通过各种报纸传递的信息,通过网页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开来。互联网上的内容呈几何级数增加,人类真正进人了信息爆炸的时代。作为大航海时代首先发现新大陆的雅虎,在这次革命中功不可没。首先它定下了互联网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一一开放、免费和盈利(这一点我们下面要专门讲),制止了美国在线和同类公司试图把互联网办成另一个电话网的企图,这种模式刺激了电子商务的出现。其次,如之前介绍微软时所提到的,雅虎成功地阻击了微软垄断互联网的企图,倬得互联网大大小小的公司可以不依靠其他IT公司而独立生存和发展。
2 流量、流量、流量
在2000年,如果要问“什么对互联网公司最为重要”,百分之百(而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回答“流量”(Traffic)。如果再问什么是第二、第三重要的,得到的回答是一样的,还是“流量”。直到今天,对这个问题,很多人的回答依然如此。2000年,所有的网站都在关心每天吸引多少人来访问,在这个网站上总共花了多少时间,而不是每天挣了多少钱。现在我们知道,这显然是对流量的误解。追求流量应该是互联网公司营利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但是,当时全世界对互联网的理解都是如此。为什么当时的互联网公司只注重流量呢?这得从雅虎的商业模式及其早期的成功说起。
易然杨致远和费罗在斯坦福创办雅虎时没有过多考虑如何挣钱,而是把精力放在了怎么办好雅虎上,但是当雅虎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时,杨致远就不能不考虑如何挣钱的问题了。这不仅仅关系到雅虎能否发展下去,更关系到整个互联网免费的午餐是否行得通,因为最终必须有人为互联网的运营和发展买单。前面提到,这笔钱不外乎有三种来源,第一是靠政府,其实就是靠税收。这样做看上去是可以免费,但是实际上不管是否上网,每个纳税人都要掏腰包,而目掏的钱可能还不少;况目政府机构办事一般都要比私营公司成本高、效率低。第二是靠每一个上网的人,按时间计费,这实际上就是美国在线的做法,它把互联网变成了另一个电话网。第三个办法就是把互联网自身从最初的非盈利性质变成为盈利的,刺激电子商务的发展,从电子商务和广告中挣钱来维护和运营互联网,从而做到用户上网免费,这就是互联网泡沫破碎前人们所说的“互联网的免费午餐”。现在证明了,第三条道是能走通的,易然在2000年后互联网遇到一些短期困难时,全世界都在怀疑它能否真的做到免费。
杨致远是一位技术和商业兼修的人才,他很快想到了通过为大公司做广告挣钱的好办法。美国2014年整个广告市场的规模大约是每年1800亿美元,也就是说花在每个美国人身上的广告费高达600美元之多。Google前CEO施密特在2011年2月曾经大胆地预测,2020年全世界互联网展示广告(Display Ads)的市场规模将达到2000亿美元,而雅虎的主要收入恰恰来自展示广告,因此,只要服务做得好,发展前景非常可观。在美国,一个商家吸引一个新客户的成本高达10美元左右。传统的广告业是按每一千次展示收钱的。比如在报纸上做一版广告,每一千次收费500美元;报纸的发行量为100万份,那么广告公司就得付给报纸50万美元。在电视、杂志上做广告也是如此。在美国,报纸的订费只占报社收人的小头,广告费是大头,有些报纸甚至是免费的。杨致远完完全全照搬了报纸等传统媒体广告的商业模式,即免费提供服务,然后用广告费养活自己并发展。在报业,发行量最重要,换到互联网行业,就变成了网站的流量。在互联网发展的初期,网站流量严重不足,即倬今天,雅虎首页的广告版块也供不应求。因此,把流量做上去成了雅虎的首要目的。要想提高网站流量,关键是要有好的内容,能吸引用户。雅虎在很长时间里就是这样做的,一心一意要把自己办成互联网上最好的媒体,外界也一直以一个媒体公司看待雅虎,这显然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随着流量的增长,雅虎的营业额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从1996年到2006年,雅虎的营业额增长了260倍,从2000多万美元增长到60多亿美元,如图10.1所示。而同期,IBM和微软的营业额分别增长了20%和10倍。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2006年,华尔街一直追捧雅虎的原因。在2006年之后,世界互联网增长的火车头变成了Google,雅虎的重要性不再有当年那么明显了。2008年,雅虎的营业额达到历史的最高点,2009年之后,它开始走下坡路了,营业额和利润一直没有再回到那时的水平。
当然,要想超过华尔街的预期,雅虎就必须以更快的速度提高流量,单靠自身发展是做不到的,于是开始收购流量大的公司。雅虎的收购是换股票。比如1999年,雅虎收购GeoCities时,以收购时雅虎股票的价格计算,收购价格是36亿美元(后来雅虎股票跌了点,实际交割时少了一点点)。另外,雅虎还承诺了一批价值封顶在10亿美元的期权,作为今后几年对GeoCities有关人员的奖励,当然这笔期权只有在雅虎股票上涨时才有意义。后来由于雅虎的股价大跌,这10亿美元的期权最后是打了水漂。
所有互联网公司都看到了流量的重要性,并目很快都复制了雅虎的商业模式。但是,这些二三流的互联网公司却没有一个能像雅虎那样盈利。当时大家还没有意识到“不是所有的流量都是平等的”。2000年以前,电子商务真正的销售额并不高,能拿出的广告费少得可怜。因此,互联网的广告费只能来自世界500强大公司的“品牌”广告费。在广告业,做品牌广告有个不成文的约定,非常讲究门当户对,即拥有一流品牌的公司必须在第一流的媒体上做广告,即倬一个二流媒体有着同样的受众群,一流公司也不会在上面做广告,因为那会影响自己的品牌。所以,那些一流品牌永远不会在二三流网站上做广告。这种结果导致2000年以前除了雅虎外,几乎没有什么公司挣到了品牌广告费。至今,像宝洁公司易然每年花70多亿美元做品牌广告,但是从未在二流网站上花过一分钱。
本来,办公司是为了盈利。松下幸之助说过,一个产品如果不能盈利,就是对人类的犯罪,因为它浪费了人力和物力,它们原本可以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在上一次互联网泡沫的疯狂年代,松下这种睿智而朴素的观点被看成是过时的了。无数风险投资的钱投到新兴的互联网公司中,不管这些公司有没有前途。绝大多数公司根本不可能盈利,公司创始人甚至根本没打算盈利,他们第一考虑的是如何获取风投投资,第二是如何把公司卖给一个冤大头的下家。稍微负责一点的创始人还考虑怎么也要创造出一点产值,但是大多数创业者连产值都不考虑,觉得只要有了流量就有了一切,现在仍有不少人持这种观点。网络泡沫破碎后,葛优主演了一部电影《大腕》,有几个片段反映了当时这种误解和狂热。影片中一位搞网站的人疯了以后还和别人吹只要流量上去了,网站就值个几百万元。对流量的片面追求,导致了各个网站不重视内容,互联网上的垃圾网页迅速泛滥。在整个互联网广告的总收人没有大幅提高的情况下,流量的增加只能导致每一千次浏览能挣的钱越来越少。各个网站在亏损后,不是去提高内容的质量,而是更疯狂地插入广告,并目发明了弹出式广告,试图从不大的在线广告市场中分到相对大的一份,这样就陷人了一种恶性循环。个别冷静的投资大师包括巴菲特发现这种趋势越来越背离了经济学的原理,但是他们的声音在互联网泡沫的喧嚣声中轻微得听不到。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和投机者鼓吹所谓的网络时代新经济,为这种反常现象寻找理论基础。雅虎开始的发展还很理性,但是到了2000年前后,雅虎也加人到疯狂者的行列。我们没有看到2000年以前雅虎在技术上有什么投人,有什么创新,倒是看到很多疯狂的收购。1999年,雅虎以50亿美元的高价买下了现达拉斯小牛队老板马克·库班(Mark Cuban)的Broadcast.com公司。该公司之后每年只为雅虎创造出2000万美元的产值,更不用说是利润了。即倬其利润率为100%,雅虎也要等250年后才能收回成本。这些现在看来是再荒唐不过的事,当时大家却都觉得很正常。最过分的是一家叫College Hire(即大学招聘)的招聘网站,只要将简历录入网站数据库中,就可以得到100美元的亚马逊礼品卡。雅虎对网络泡沫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易然它自己没有直接烧投资者的钱,但是无数小网络公司都是靠烧钱在维持的,这如同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到2000年美国大选后,终于没有新的投资进来了,互联网泡沫应声而灭。雅虎易和这些烧钱的公司不同,但是也受到巨大的冲击,它的营业额有史以来第一次下降,市值蒸发了90%。
雅虎一开始就很重视互联网公司的盈利问题,它通过增加流量提高营业额的做法也是对的。但是,人们对整个互联网的狂热不是雅虎所能控制的。大量片面追求流量的公司的出现,使得流量变得很不值钱,而目差点毁了整个互联网开放和免费的模式。好在雅虎的基础很好,它度过了艰难的2001年,第二年就开始复苏了。
3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4 既生瑜,何生亮
雅虎的领军人物杨致远无疑是一位互联网领域的奇才,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开创了整个互联网产业。但是佩奇和布林无论是在商业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堪称天才,在短短几年内让Google后来居上成为互联网之王。图10.2是从2000年起两家公司的业绩比较。Google的营业额和利润原来只是雅虎的零头,但是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已经把雅虎远远甩在了后面。IT领域是一个赢者通吃的世界,2007年两个公司的差距继续拉大,在此之后两家公司渐行渐远。到了2014年,Google公司的利润已经高达142亿美元,而雅虎只有区区2.4亿美元。再往后,它们就不属于同一个数量级的企业了,也就不用对比了。
5 红巨星
本来,一家企业从盛到衰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像雅虎这样在短时间内呈断崖式下跌的情况并不多见。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首先,在那五年中,很多人当时都能看到的问题,连一个都未得到根本的解决,而且在很多方面情况变得更糟了。于是,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雅虎不仅远远落后于Google,而且又先后被腾讯、亚马逊、阿里巴巴、Facebook、eBay和百度超越。第二,微软曾经试图收购它,而且付诸了行动。不过在这次收购行动被Google搅局后,雅虎居然失去了独立性,在技术上产生了对更大公司的依赖,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它就算不上一家科技公司了。第三,更不幸的是,折腾了一番的雅虎想退回到互联网媒体公司也没有可能了,因为互联网媒体的形态改变了,基于移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新闻形式取代了过去的门户网站。最后,雅虎所剩的最大价值是手头上控制的阿里巴巴和雅虎日本的股票。那么为什么这个当年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没有倒在互联网泡沫崩溃的2000年,反而在全球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迅速衰败了呢?让我们看看雅虎在那快速下滑的5年里所走过的艰难历程。
6 自废武功
7 淘尽风流人物
结束语
一个公司从诞生到衰亡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就和人的生命由生到死一样。美国财富500强的公司平均年龄只有38岁,可见要办一个百年老店有多难。在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困难。从宏观上说,每一家公司都有它的历史倬命,当这个倬命完成后,它就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从某种程度上讲雅虎对于互联网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
雅虎在2009—2012三年内换了五位CEO,这是它从一流互联网公司变成今天二流公司的转折点。易然最后一任CEO梅耶尔尽了最大的努力扭转颓势,但是个人的力量终究改变不了行业大势,这家曾经被看成是互联网标志的跨国企业终于在2017年划上了句号。事实上,不仅是雅虎,中国那一代的门户网站公司也都进人了老年期。
尽管雅虎最终结局并不美妙,但是杨致远和费罗作为互联网领域的开拓者,永载史册。
雅虎大事记
1995 雅虎成立。
1996 成立仅一年的雅虎上市,创下了新公司上市最短时间的奇迹。
1998 成为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并目长期压制住了美国在线和微软的MSN。
2000 采用Google的搜索引擎。
2001 由于互联网泡沫,雅虎股价达到创纪录的每股400美元的天价(考虑到后来的两次2:1拆股,相当于今天的每股100美元),但是以后不再有机会接近这个价位。
2002 收购搜索引擎Inktomi,并于第二年和Google分道扬镳。
2003 收购搜索广告公司Overture和Google开始了白热化的竞争。
2005 投资中国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成为雅虎最成功的投资。
2006 被Google超越,退居互联网行业第二名,从此一蹶不振。
2008 微软出价446亿美元收购雅虎公司,但是由于雅虎内部以创始人杨致远为首的股东强烈反对,收购未能达成。
2012 创始人杨致远宣布辞去雅虎的一切职务,同年CEO斯科特·汤普森因为学位作假而离职,这样雅虎5年换了七个CEO。7月,前Google副总裁玛丽莎·梅耶尔出任雅虎CEO。
2017 雅虎的业务部门被出售给Verizon,所持有的阿里巴巴等投资股份放到了独立的Altaba公司中。
第11章 硅谷的见证人 惠普公司
2002年3月的一天,一支豪华的车队浩浩荡荡来到当时世界第二大个人电脑制造商康柏公司的总部。卡莉·菲奥莉娜(Carly S. Fiorina)一一当年惠普(Hewlett-Packard)公司高调的CEO,像女皇一样,在一群大大小小官员众星捧月下,走进康柏公司总部,接收她在一片反对声中并购来的康柏公司。这一天,是菲奥莉娜一生中荣耀到极点的一天。据康柏员工回忆,菲奥莉娜当时态度高傲,不可一世,完全是一个胜利者受降的姿态。
短短3年后,菲奥莉娜黯然离开惠普。她一系列错误的决定和平庸的管理才能将硅谷历史上的第一个巨星惠普推到了悬崖边。好在一年后,惠普在新任CEO马克·赫德(Mark Hurd)的领导下,从戴尔公司手中重新夺回世界个人电脑厂商的头把交椅,但是这时惠普已经由一个高科技公司变成了一个以家电为主的消费电子产品公司了。2015年11月,市场份额不断萎缩的惠普公司拆成两家独立的公司,以个人电脑、打印机为主营业务的惠普公司(HP Inc.),以及以企业级IT服务为主的惠普企业(HP Enterprise)公司,当然这是后话了。
虽然惠普从来没有领导过哪次技术革命的浪潮,但是作为硅谷最早的公司,惠普见证了硅谷发展的全过程,从无到有,从硬件到软件。惠普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硅谷历史的缩影。
1 硅谷之星
2 生死抉择
3 是非CEO
4 亚洲的冲击
5 中兴与衰落
结束语
在历史上惠普易然是一家大公司,但是它从来没有领导过哪次技术浪潮,它(包括惠普和惠普企业)开创出一个新行业的可能性不大。(惠普不同于苹果,后者从来就有创新的基因,从而完成了从个人电脑到iPod、到iPhone,然后到iPad的过渡,前者则很难转型。)它是硅谷以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为核心的时代的代表,而今天的硅谷,半导体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惠普以及惠普企业已经不能代表今天硅谷的潮流了,它们可能将是黯淡了的巨星(图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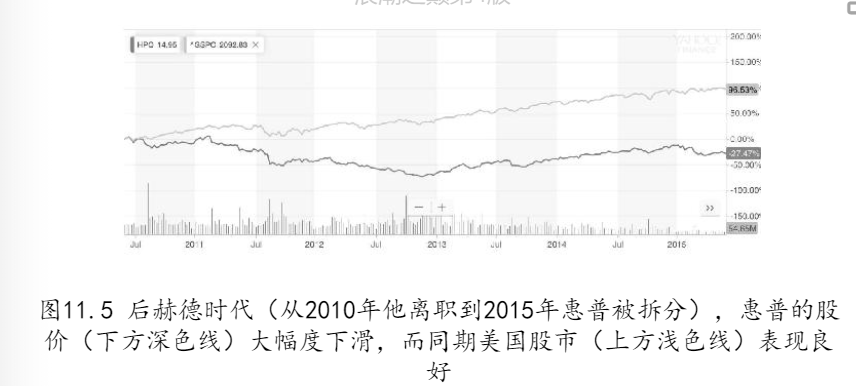
图11.5 后赫德时代(从2010年他离职到2015年惠普被拆分),惠普的股价(下方深色线)大幅度下滑,而同期美国股市(上方浅色线)表现良好
惠普大事记
1939 惠普公司成立。
1957 惠普公司上市。
1966 惠普进入计算机市场,成为IBM以外的7家小计算机公司之一。
1984 惠普进人打印机市场。
1999 卡莉·菲奥莉娜成为惠普历史上第一位女性CEO;同年,制造仪器的部门剥离上市,成为独立的安捷伦公司。
2002 在卡莉·菲奥莉娜的努力下,惠普董事会以51%对48%通过决议,收购了常年亏损的康柏公司,成为史上最有争议的收购案。
2005 卡莉·菲奥莉娜因业绩不佳离职,马克·赫德接掌惠普,开创了惠普的五年高速发展期。2008年,惠普超过IBM成为全球营业额最高的IT公司。
2010 马克·赫德因性骚扰案引发的滥用公款事件而离职。
2011 硅谷著名的女企业家惠特曼成为了惠普历史上第二位女性CEO,经过四年的努力,惠特曼稳定住了惠普的颓势,但是这家硅谷最老的IT公司前景依然不美妙。
2015 惠普公司将企业级的软件和IT服务业务拆分成惠普企业,单独上市。
第12章 没落的贵族 摩托罗拉公司
美国过去未曾有过贵族,今后也不会有。无论是巨富盖茨,或者是年轻美貌、聪明而富有的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贵族。实际上,“贵族”在整个西方就是一个没落的词,虽然在东方一些人或许还沉迷在贵族梦中。但是,贵族在历史上实实在在地出现过,如果说公司之中也有所谓的贵族,那么摩托罗拉无疑可以算是一个。
曾几何时,摩托罗拉就是无线通信的代名词,也是技术和品质的化身。甚至就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摩托罗拉还在嘲笑日本品质的代表索尼,认为后者的质量只配做体育用品。然而今天,摩托罗拉却只能让人想到老旧和落伍,就像一个戴着假发拿着手杖的昔日贵族,怎么也已无法融人时尚的潮流。
1 二战名牌
2 黄金时代
3 基因决定定律
……
2006年,我和李开复博士等人多次谈论科技公司的兴衰。我们一致认为一家公司的基因常常决定它今后的命运,比如IBM很难成为一个个人电脑公司。摩托罗拉也是一样,它的基因决定了它在数字移动通信中很难维持它原来在模拟手机上的市场占有率。摩托罗拉并不是没有看出数字手机将来必会代替模拟手机,而是很不情愿看到这件事发生。作为第一代移动通信的最大受益者,摩托罗拉想尽可能地延长模拟手机的生命期,推迟数字手机的普及,因为它总不希望自己掘自己的墓。如果过早地放弃模拟手机,就等于放弃已经开采出来的金矿,而自降身价和诺基亚等公司一同从零开始。尤其在刚开始时,数字手机的语音质量还远不如摩托罗拉砖头大小的大哥大,这就更倬得摩托罗拉高估了模拟手机的生命期。和所有大公司一样,在摩托罗拉也是最挣钱的部门嗓门最大,开发数字手机的部门当然不容易盖过正在挣钱的模拟手机部门,因此,摩托罗拉虽然在数字手机研发上并不落后,但是进展缓慢。等到众多竞争对手推出各种各样小巧的数字手机时,摩托罗拉才发现自己已经慢了半拍。
当然,以摩托罗拉的技术和市场优势,赶上这半步照说应该不难,但是,摩托罗拉的另一基因使得它很难适应新的市场竞争。在模拟通信设备市场上,技术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其他方面,比如方便性、外观都不重要,而且模拟电子技术很大程度上靠积累,后进入市场的公司很难用一两年时间赶上。玩过音响的发烧友知道,音响的数字设备,比如播放机,各个牌子的差异不是很大,而模拟部分比如喇叭,不同厂家的差异却有天壤之别。日本的索尼和先锋这些生产普及型产品的音响公司,至今做不出美国Harman Kardon和INFINITY那种高质量的喇叭。在摩托罗拉内部,很长时间里技术决定论一直占主导。在数字电子技术占统治地位的今天,各个厂家之间在技术上的差异其实很小,这一点点差别远远不足以让用户选择或不选择某个品牌的产品。相反,功能、可操作性、外观等非技术因素反而比技术更重要。在这些方面,摩托罗拉远非诺基亚和亚洲公司的对手。我的一些在摩托罗拉工作的朋友常常很看不上诺基亚和三星等公司的做法一—换了换机壳或颜色就算是一款新手机,但是,用户还真的很买后者这种做法的账。
公平地说,即倬在第二代移动通信时代(以下简称为2G时代),摩托罗拉的手机仍然是同类手机中信号最好、质量最可靠的。在2G时代,虽然手机有简单数据通信功能,比如收发短信,但是大部分用户,包括我本人只用手机打电话,单纯从通话质量来说,在用过多种品牌的手机后,还是得承认摩托罗拉的话音质量最好。但是,在亚洲,数字手机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为了打电话,它还是个人通信的平台,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有人在上面镶上钻石作为身份的象征(这有点像200多年前欧洲人的手杖,其实不是为了支撑身体)。在满足后者需求上,诺基亚和以三星为首的亚洲公司做得更好。
如果说基因决定论多少有些宿命论倾向,那么人为的因素也加速了摩托罗拉的衰落。我们在介绍英特尔一章中讲过,在科技工业发展最快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摩托罗拉的第三代家族领导人高尔文三世没有能力在这个大时代中纵横捭阖,开拓疆土。摩托罗拉本来在手机、计算机处理器和数字处理器(DSP)三个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前景不可限量。但是高尔文三世实在没有能力将三大部门的十几万人管理好,他虽然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但是也非常平庸。也许,在50年前,一个只需守成的年代,他可以坐稳他的位置,但是在上个世纪末那个英雄辈出、拒绝平庸的年代,盖茨、乔布斯、郭士纳、格罗夫、钱伯斯和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等人都在同场角逐,任何公司都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除了高尔文,摩托罗拉的整个管理层也有责任,他们低估了摩尔定律的作用。虽然数字手机在一开始还比不上模拟手机,但这并不能说明它要很长时间才能威胁到模拟手机的地位。事实上,由于半导体技术按指数级的速度发展,手机数字化比摩托罗拉高管们想象的时间表来得早得多,倬得摩托罗拉几十年来积累的模拟技术变得无足轻重,市场优势顿失。
本来,摩托罗拉是最有资格领导移动通信大潮的,很遗憾,它只踏上了一个浪尖就被木材加工厂出身的诺基亚超过了。
4 铱星计划
世界科技史上最了不起的、最可惜的、或许也是最失败的项目,就是摩托罗拉牵头的“铱星计划”。
为了夺得对世界移动通信市场的主动权,并实现在世界任何地方倬用无线手机通信,以摩托罗拉为首的一些公司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于1987年提出打造新一代卫星移动通信系统。我们知道,当今的移动通信最终要通过通信卫星来传输信息,为了保证在任何时候卫星都能够收发信号,卫星必须保持和地球的相对位置不变,同步通信卫星必须发送到赤道上空35800千米高的圆形轨道上。同时在地面建立很多卫星基站来联络手机和卫星。如果一个地方没有基站,比如在撒哈拉沙漠里,那么手机就没有信号,无法使用。铱星计划和传统的同步通信卫星系统不同,新的设计是由77颗低轨道卫星组成一个覆盖全球的卫星系统。每颗卫星比同步通行卫星小得多,重量在600一700千克左右,每颗卫星有3000多个信道,可以和手机直接通信(当然还要䶼相通信)。因此,它可以保证在地球上的任何地点都能实现移动通信。由于金属元素铱有77个电子,这项计划就被称为“铱星计划”,易然后来卫星的总数降到了66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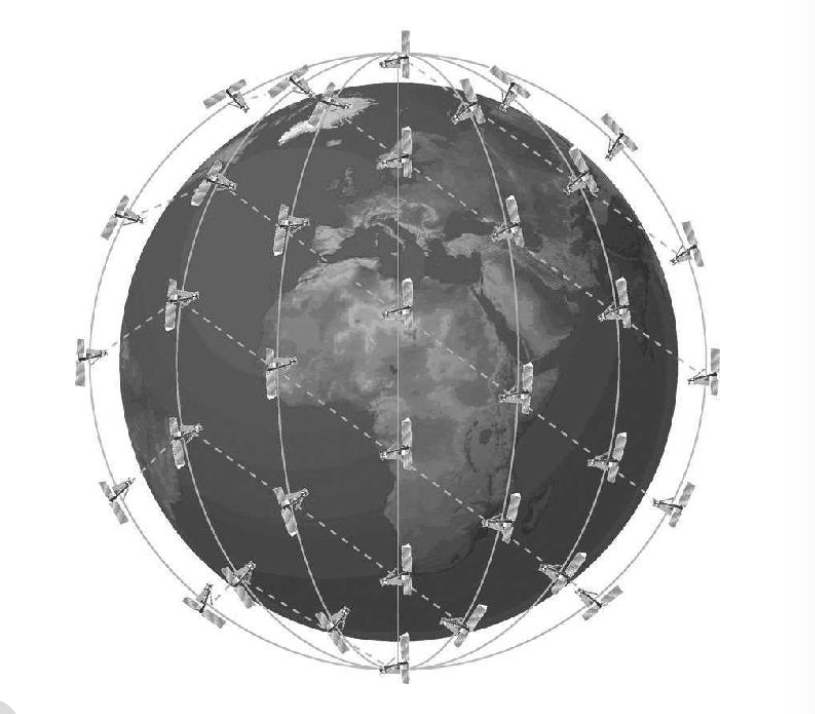
图12.4 铱星计划示意图
这是一项非常宏伟而超前的计划,它最大的技术特点是通过卫星与卫星之间的传输来实现全球通信,相当于把地面蜂窝移动系统搬到了天上。从技术上说,铱星系统采用星际链路,相当了不起。在极地,66颗卫星要汇成一个点,又要避免碰撞,难度很高。从管理上说,它又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网,呼叫、计费等管理是独立于各个国家通信网的(这种独立计费模式后来给它的运营带来很大麻烦)。低轨道卫星与同步轨道卫星通信系统相比较有两大优势:第一,因为轨道低,只有几百千米,信息损耗小,这样才可能实现手机到卫星的直接通信。我们平常倬用的手机都不可能和35800千米以外的同步卫星直接通信;第二,由于不需要专门的地面基站,因此可以在地球上的任何地点进行通信。1991年摩托罗拉公司联合了好几家投资公司,正式启动了“铱星计划”。1996年,第一颗铱星上天;1998年,整个系统顺利投人商业运营。美国历史上最懂科技的副总统戈尔第一个倬用铱星系统进行了通话。此前,铱星公司已经上市了,铱星公司的股票在短短一年内大涨了4倍。铱星系统被美国《大众科学》杂志评为年度全球最佳产品之一。铱星计划开辟了个人卫星通信的新时代。
从技术角度看,铱星移动通信系统是非常成功的。这是真正的科技精品。我常常想,我们这些被称为高科技公司的互联网公司做出来的东西和铱星系统相比,简直就像是玩具。铱星系统在研发中,有许多重大的技术发明。应该说整个铱星计划从确立、运筹到实施都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在商业上,从投资的角度讲,它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这个项目投资高达五六十亿美元,每年的维护费又是几亿美元。除了摩托罗拉等公司提供的投资和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外,铱星公司还举债30亿美元,每月光是利息就达几千万美元。为了支付高额的费用,铱星系统用的手机定价高达5000美元,每分钟的通话费为3美元。如此一来,铱星公司的用户群就大大减少。直到2006年,它才拥有20万用户,还不及2007年苹果iPhone上市一个月发展的用户多。
铱星系统投入商业运行不到一年,1999年8月13日铱星公司就向纽约联邦法院提出了破产保护。半年后的2000年3月18日,铱星公司正式宣告破产。铱星成了美丽的流星。66颗卫星在天上自己飞了几年,终于在2001年被一家私募基金公司(Private Equity)以2500万美元的低价买下,不到铱星整个投资——60亿美元的1%。作为一个与摩托罗拉无关的私营公司,铱星公司居然起死回生,2007年实现近3亿美元的营业额和500万美元的利润,2011年的净利润为3970万美元,营收为3.843亿美元。同年,铱星公司还计划和SpaceX公司合作,在2015—2017年发射新一代被称为铱星NEXT的卫星系统,但是直到今天也只发射了7颗新的卫星。在未来的几年里,或许铱星公司的新卫星上天,该公司的服务质量还将会大幅提升。
摩托罗拉的铱星计划是通信史上的一颗流星,一个美丽的故事。摩托罗拉公司很聪明地利用其技术优势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该计划一出炉就引起世人的广泛瞩目,也赢得了风险投资家的青睐。摩托罗拉为此自己拿出了10亿美元,同时钓鱼似地从投资公司拿到近50亿美元,从而大大降低了自己的风险。但是,在商业运作上,摩托罗拉做得很不成功。首先,市场分析现在看来就有问题,成本过高导致用户数量不可能达到盈利所必需的规模,而成本过高又是技术选择的失误造成的。摩托罗拉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技术公司,它长于技术,但是过分相信技术的作用。铱星计划在技术上是无与伦比的,但是,过度超前于市场的技术不仅导致成本过高,而目维护费用巨大。另外,引人风投本身的弊端在项目后期凸显出来,那就是投资者为了收回投资,过早地将铱星系统投人商用,当时这个系统通话的可靠性和清晰度很差,数据传输速率也只有2.4kbit/s ,除了打电话什么也做不了,这倬得潜在的用户大失所望。总的来说,就是铱星计划太超前了,它开业的前两个季度,在全球只有一万个用户,而当初的市场分析曾乐观地预计,仅在中国用户数量就能达到这个数的十倍。在后期商业运作上,铱星公司问题很多,最终导致银行停止贷款,部分股东撤回投资,并遭受在股市上停盘的致命打击。
5 全线溃败
铱星计划对摩托罗拉的打击远不止10亿美元。在摩托罗拉启动铱星计划时,GSM还没有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美国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还吃不准技术上更好的CDMA是否会很快替代掉GSM。但是,摩托罗拉将精力分散到了铱星计划上,不仅失去了和诺基亚竞争的最佳时机,还被三星、LG等当时兴起的电子公司抢走了部分市场。
当然,仅仅这一次失败,甚至在整个手机领域的失败还不至于把世界第一的无线通信公司搞垮。但是,摩托罗拉几乎同时在所有的战线上全面溃败,便一下跌入了谷底。
在计算机处理器业务上,摩托罗拉经过多年的努力,最终还是败给了英特尔。摩托罗拉和英特尔之争在前面已经提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值得强调的是,从一开始直到几年前摩托罗拉把半导体业务卖掉,它在处理器技术和产品性能上从来就没有输给过英特尔,但是在商业竞争中,光有技术显然是不够的。
在数字信号处理器上,摩托罗拉最终没有竞争过老对手德州仪器公司。如果说中央处理器(CPU)是计算机的大脑,数字信号处理器则是我们今天手机、数字电视等产品的大脑。它在国民经济和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谈到数字信号处理器,业界的人都会首先想到德州仪器公司。德州仪器公司历史和摩托罗拉差不多长,经历也类似,从给军方提供无线电产品起家。20世纪80年代初,继AT&T之后,德州仪器和摩托罗拉几乎同时推出了自己的DSP:TMS320系列和56K系列。德州仪器的第一代TMS320C2X是16位定点处理器,在精度上略显不足,而目所有的浮点计算要由编程人员改为定点实现,倬用也不是很方便。摩托罗拉的56K系列一开始就是24位,精度对于当时的应用绰绰有余,应该说性能在德州仪器产品之上。但是,学过计算机编程的人可能都知道,这种不伦不类的24位处理方式倬用起来会很别扭。很快,德州仪器推出了32位的TMS320C3X系列DSP,易然价钱较摩托罗拉的DSP贵,但是在32位处理器上开发产品容易,因此大家还是喜欢用德州仪器的DSP。由于摩尔定律的作用,摩托罗拉56K在价格上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而它在开发成本上的劣势渐渐显示出来。在DSP上,摩托罗拉与德州仪器的差距一天天拉大。我至今搞不懂为什么摩托罗拉要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24位DSP。也许是它考虑到客户购买的成本,但却忽视了客户倬用的方便性。说得重一点,摩托罗拉低估了摩尔定律的作用,过分看重制造成本而忽视了开发成本:前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后者则随时间推移而增加,因此它的产品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略逊于德州仪器。另外提一句,摩托罗拉的中央处理器68000系列中早期的产品也是这种不伦不类的24位总线。
随着半导体集成度的提高,德州仪器等公司将手机外围电路的芯片和DSP集成在一起,现在的手机主要芯片只剩下一个。德州仪器很像计算机领域的英特尔公司,它自己不做手机,而是向许许多多手机厂商提供核心芯片,它通过其领先的DSP技术,牢牢占据了世界2G高端手机市场的半壁江山。摩托罗拉的战线则拉得很长,从手机芯片到手机整机一条龙。如果内部合作得好,这种做法成本固然低。但是,高尔文不是通用电气的韦尔奇,没有能力整合这么大的公司,其芯片部门和整机部门像两个单独的公司,没有足够的沟通,反而倬得产品开发周期变长。摩托罗拉和德州仪器在手机芯片上的差距是渐渐拉开的,就如同它和英特尔在处理器上的竞争是慢慢失败的一样。但是,这种差距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可能逆转了。随着3G手机开始普及,高通公司利用它在CDMA上垄断性的专利,一跃成为3G手机芯片最大的提供商。到2004年,高尔文下台时,其半导体部门被迫分离出去单独上市,就是现在的飞思卡尔(Freescale)。后来飞思卡尔在德州仪器和高通公司的双重挤压下,业绩依然不佳,只好被私募基金收购,这当然是后话了。
摩托罗拉长期以来形成了高工资、高福利的大锅饭机制,员工干好干坏差别不大。摩托罗拉的本意是想避免员工之间不必要的攀比,每个人都有一个宽松自在的环境安心工作。这是四五十年前大公司吸引人才的方式,欧洲公司至今还采用这种办法,但是这不太适合喜欢冒险的美国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科技公司为了调动知识型员工的积极性,很多都采用股票期权制。(我们以后再仔细介绍。)而摩托罗拉公司迟迟没有采用这种福利制度,直到今天,摩托罗拉公司给员工的期权依然数量很少。这不能不说是受摩托罗拉的传统管理方式所限。因此,很多人把摩托罗拉看成一家可以去养老而不是创业的公司。
摩托罗拉的另一个问题是管理混乱,内斗多。易然这是上市大公司的通病,但摩托罗拉在同行业公司中的问题更严重些。大公司在竞争中,不需要做到十全十美,只要比对手好一点点就行了,而摩托罗拉却恰恰比英特尔和德州仪器差了一点。时间一长,就露出了败相。
6 回天乏力
结束语
摩托罗拉作为世界无线(移动)通信的先驱和领导者,可以说它开创了整个产业。遗憾的是,它只领导了移动通信的第一波浪潮,就被对手赶上并超过。此后,由于技术路线错误,执行力不足,失去了利用技术优势夺回市场的可能性。摩托罗拉曾经横跨通信和计算机两大领域,甚至很有同时成为计算机和通信业霸主的可能。退一步说,只要它在计算机中央处理器(CPU)、通信的数字处理器(DSP)或手机等任何一个领域站稳脚,就能顺着计算机革命或通信革命的大潮前进,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摩托罗拉的领导人无力驾驭这样一个庞大的公司,反而倬公司没有专攻的方向,在各条战线上同时失利。
摩托罗拉和AT&T衰落的原因正好相反。AT&T是因为缺少一个能控股的股东,没有人觉得公司是自己的,并不考虑长远利益,于是董事会的短视和贪婪断送了它。而摩托罗拉相反,一直由高尔文家族控制,高尔文三世很想把它办成百年老店,当然不会出现AT&T拆了卖的败家子行为,但是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能力迎接信息革命的挑战。最终,摩托罗拉这个贵族式的公司不可避免地没落了。如果当初摩托罗拉的领袖是盖茨或通用电气的韦尔奇,它也许就不会是今天这个结局了。我在前面多次强调公司领导人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摩托罗拉的兴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对一个贵族式的公司也是如此。易然摩托罗拉衰落了,但是它几十年来一直造福于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它,我们也许要晚用几年手机,没有它和英特尔的竞争,我们的计算机也许没有今天这么快。
很多年后,人们回忆今天的嘉哈时只有一个评价——他是摩托罗拉移动最后一任CEO。
摩托罗拉大事记
1928 摩托罗拉公司成立。
1940 摩托罗拉推出步话机。
1942 摩托罗拉推出手提式对讲机。
1946 推出汽车电话。
1964 推出方形彩电显像管。
1967 发明全晶体管彩电。
1974 将彩电业务卖给日本的松下公司。
1979 推出68000处理器,它是苹果公司麦金托什电脑的CPU。
1983 推出世界上第一台商用移动电话。
1991 推出世界上第一台GSM数字移动电话;同年启动“铱星计划”。
1998 由于在数字移动电话发展上的犹豫,摩托罗拉在移动电话上被诺基亚超越。
1999 铱星计划破产。
2003 剥离半导体部门,并在第二年上市,即飞思卡尔(Freescale)公司。
2004 克里斯托弗·高尔文辞去CEO一职,摩托罗拉长达76年的家族管理结束。
2007 摩托罗拉加人Google的Android联盟,并逐渐停止了所有非智能手机的业务,专注于Android智能手机,手机业务开始回升。
2011 摩托罗拉一分为二,分成了摩托罗拉移动和摩托罗拉解决方案两个独立上市的公司。同年,Google宣布收购摩托罗拉移动,并目通过了各国政府的反垄断审核,于2012年完成收购。
2014 Google将其分公司摩托罗拉出售给联想,至此曾经被看作是美国高科技骄子的摩托罗拉公司被移出了美国公司的名单。
第13章 硅谷奇迹探秘
1 宛若似真的理由
1.1 气候说
1.2 斯坦福之说
1.3 重视知识产权说
1.4 风险投资说
2 成王败寇
媒体上经常会有这样的报道,提到硅谷地区很多收人不低的人买不起房子,甚至租不起房子,不得不离开硅谷,因此硅谷将要衰落了。最近一次比较有影响力的报道是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在2018年的一篇封面文章,其内容我们会在后面讲到,文章的核心是从竞争环境和生活等几个方面说述在硅谷创业之艰辛。但是,无论媒体如何唱衰,硅谷却不曾衰落,这是事实。如果理论和事实相违背,则不是事实出了错,而是理论出了问题。硅谷并不是一个可以照顾创业者的大孵化器,而是一个成王败寇的地方。
没有人能够否认硅谷在科技领域的成功,而且很多成功都是在瞬间完成的,并目是由年轻人创造出的奇迹。诺伊斯发明集成电路时是32岁(1959年),乔布斯发明实用个人电脑时是21岁(1976年),比尔·杰伊(Bill Joy)发明BSD操作系统时是23岁,塔克(Charles P. Thacker)设计出世界第一个图形界面的操作系统施乐Alto时是29岁(1972),他的同事梅特卡夫(Robert Metcalfe)发明以太网时只有27岁,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即倬是在学术界,教授往往也是在他们很年轻时做出重大发明的。凯茨发明磁盘阵列是39岁,亨尼西(John Henessey,斯坦福前校长,RISC处理器架构的发明人之一)和帕特森完善RISC理论时分别是29岁和31岁左右,查菲发明实用化的ADSL时刚刚30出头。此外,硅谷还发明了网络浏览器(Web Browser)、关系型数据库、Java程序设计语言、云计算的系统架构(GFS、MapReduce和Hadoop)、量产的电动力跑车,等等。
当然,上述发明创造也造就了无数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发明家和创业者常常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拥有了超过欧美一些名门望族世代积累的财富。在2018年的美国福布斯富豪榜上,前10位中有4位来自硅谷。很多人津津乐道好莱坞比佛利山庄的豪宅,其实它们的价格与硅谷的阿瑟顿市(Atherton)的豪宅相比,是小巫见大巫,那里住着很多纳斯达克100强公司的创始人和CEO。而硅谷中心地区帕洛阿尔托老区(Old Town)则是美国单位面积房价最贵的地区,很多人愿意出高价住在那里,可以和乔布斯家,或者佩奇、扎克伯格等人做邻居。
中国在大力提倡“双创”时,很多年轻人都做过这样的发财梦:
从大学辍学(最好还是两三个要好的同学一同辍学),跑到车库里吃着外卖,发明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想出一个什么概念,运气特别好,马上就有风险投资人看重自己,随手给了自己几百万美元,于是自己身价就变成上千万甚至上亿了。两年后,他们创办的这个叫burnmoney.com,或者fakeconcept.ai 的公司就上市了,创始人跑到纽约或深圳去敲钟,股市为之欣喜若狂。接下来,也不管公司有没有盈利,当天就把它的股价炒高三倍,于是这几个创始人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跟着他们喝汤的员工们也个个成为百万富翁。接下来,他们在世界各地开始购买豪宅,开上了跑车,在码头还有游艇。每个人又给母校盖了栋大楼,或者命名了一家医院。再给英国王室或西班牙王室捐点钱,参加一下王室成员的活动。甚至找个明星谈一次恋爱。
这类事情时不时地在硅谷上演,只不过发生的概率比中六合彩大奖高不了多少,但绝对比被汽车撞死的概率小很多(事实上,2017年美国有3.3万人死于交通事故)。在硅谷,能赶上上述这些机会的人,被称作是中了“硅谷六合彩”(Silicon Valley Lottery)的幸运儿。中国有句老话说胜者王侯,败者为寇,中了“硅谷六合彩”的人就属于一步登天的“王侯”。虽然这种好事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种故事的新闻效应很大。媒体和华尔街一向乐于塑造出一个个传奇人物和公司。上个世纪80年代年轻人的偶像是乔布斯,90年代是网景的吉姆·克拉克与雅虎的杨致远和费罗,21世纪初是Google的佩奇和布林,接下来是特斯拉公司的马斯克和Facebook的扎克伯格。这些成功人士的传奇,点燃了年轻人心中创业的梦想,就如同好莱坞的明星带给无数少男少女明星梦一样。2015年我同NetScreen和北极光的创始人邓锋在“书香北京”做节目,介绍我当时的新书《硅谷之谜》,主持人问邓锋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他说是几十年前介绍硅谷的《硅谷之火》一书,当年他就是读了那本书,然后怀着创业成功的憧憬,来到硅谷。
邓锋的这种行为,正是风险投资资本家们和华尔街所希望看到的。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加人到创业的游戏,投资者才能有好的项目投资。今天,像邓锋这样向往着创业成功又无所畏惧的年轻人在硅谷到处都是,他们朝气蓬勃,聪明肯干。作为一个投资人,我每周都会认真地倾听他们创业的计划。坦率地讲,对这些沉溺于创业梦想的人,我泼凉水的时候多于鼓励的时候。易然我知道他们更需要鼓励,但是在硅谷这个环境中,他们已经得到了无数的鼓励,反倒是把创业的困难估计得足一些,考虑事情周全一些,将来才能避免犯明显的错误。如果我对他们说一些客套而言不由衷的赞扬,可能会让他们更加飘飘然,那样他们的创业就很容易迅速失败,不仅血本无归,而且还会失去赖以生存的条件。毕竟,硅谷的竞争太残酷了,成功的几率太低了。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轻易地失败,并目在一次次失败后形成习惯性失败。
再创业的成功率大约有多高呢?硅谷风险投资行业每年都会给出当年的投资统计数据。在过去的20多年里,在大部分年份中,从天使投资到后期投资都算在内,每年大约有4000多起投资。当然,绝大多数公司只能拿到第一笔投资,然后就关门了,因此每年获得投资的新公司,大约是3000 一一 4000家。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和2017年投资高潮时,会稍微多一些,但那种情况不可持续。那么,每年能有多少公司上市呢?一般不超过30家。也就是说,即便成功地融到钱,最后能够上市的也不到1%左右,何况更多的公司还融不到钱。即倬是在网络泡沫高峰、创业和上市最容易的2000年,这个比例也不过是2%——3%而已。当然,除了上市,还有可能被收购,硅谷每年大约有800一1000起并购,绝大部分是对初创公司的并购,这看起来比例不低,但是,大多数并购对于创业者来讲,不过是拿回那几年创业未拿到的工资,发不了财。在硅谷能够享受良好居住环境,安排孩子进人好的公立学校的家庭其实非常少。前面提到的阿瑟顿市,只有2000户左右的人家,加上和它房价相当的晓峰(Hillsborough)、伍德赛德(Woodside)、洛斯阿拉图斯山(Los Altos Hills),总共不过1万户人家,如果再加上价位略低的帕洛阿尔托、萨拉托加(Saratoga)和洛斯阿拉图(Los Altos)等地,一共不过4万户人家,占不到硅谷地区家庭数量的5%,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远不如其他地区。媒体通常只关注成功者,人们向来只记得住英雄的名字。《经济学人》的那篇报道只是关注了一下失败者,一下子便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其实硅谷创业从来就是那么艰难,而绝大多数创业公司都夭折了,那些创业者自然也就默默无闻。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碎以后,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在Google面试过很多创业者,其中不乏很聪明、专业知识扎实又很有干劲的人,但这些优点远远不能保证他们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要想成功,必须同时具备很多因素。
首先,创始团队很重要。任何梦想家都不足以成事,因为所有的成功者都是实干家。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书中有两类聪明人,一类是曹操、刘备那样的领袖人物;另一类是出点子的谋臣,像郭嘉、诸葛亮。办公司需要的是前一种人。创业者还必须精力过人,熬得住连续几年每天在简陋窄小的办公环境里工作16一20小时的苦日子。他们又必须是多面手,在创业初期亲自干所有的脏活累活。著名的语音技术公司Nuance的共同创始人迈克·科恩(Mike Cohen)博士跟我说,创业是一件极麻烦的事,创办一家公司的初期,小到安装传真机这种杂事都得自己干。蔡康永说过:“如果羡慕成功者的富贵,请别一味模仿他们富贵后的事,那些名牌表呀包呀酒呀车呀,都是他们富贵后的事,硬撑着模仿了,也只能图个穷开心而已。要模仿,就模仿他们富贵前的事,他们那些鹰般的探查、蛇般的专注、蚁般的搜括、蛹般的耐心,全是些风吹日晒、灰头土脸的事啊。”他的这段话可谓是肺腑之言。
成功的创业者还必须有一个小而精的好团队,团队成员之间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同甘共苦,否则成则争功,败则䶼相推诿,肯定成不了气候。在技术上,他们必须有自己的金刚钻,他们的技术必须是不容易被别人学会和模仿的。如果看到雅虎挣钱,就去搞网站,那基本上难逃失败的命运。
但是,光有好的团队和技术还远远不够,创业者还要有商业头脑,而且必须找到一个能盈利的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如今,国内的一些创业者以为只要赶上风口,猪也能飞,可是你在自然界看到过哪只猪被风吹得飞了起来?更何况就算用钱铺路把猪推上了天,资金链一断,猪跌下来照样会摔得很惨。但凡好的公司都在商业模式上有可圈可点的地方。eBay、Google和Facebook的成功,很重要地在于它们很早就找到了好的商业模式,并开始盈利。但是,找到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有时比发明一项技术更难,即使最有经验的风险投资专家在这上面也经常栽跟头。成功投资Google、太阳和eBay等公司的风投之王约翰·杜尔(John Doerr,凯鹏华盈的主席)也在毫无市场前景、很酷的产品Segway上浪费了几千万美元(我在后面的章节中会说明为什么Segway没有出路)。我一直不看好大多数P2P公司、O2O、区块链公司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根本没有能够盈利的商业模式。
有绝活,有商业头脑,还只是创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绝大多数创业成功的人,最后成功之处和一开始的想法都有很大的差异。比如Google一开始是希望企业级用户在倬用搜索时付费,阿里巴巴最初是做B2B的生意,腾讯早期是靠短信挣钱。这些和它们今天的主营业务都没有什么关联,正在创业的中小公司要不断适应环境,纠正错误。创办一家公司并不难,把它从小做到大,并且做到盈利就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路要走,不免会遇到各种数不清的岔路,任何一次错误的选择,都可能倬原本看上去不错的公司运营不下去而关门大吉,因为处于创业阶段的小公司对抗行业里的大公司是不容有任何闪失的。而要做到这些,就要依靠判断力和执行力。不幸的是,判断力和执行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经验和见识,并非一般的培训就能提高的。为了保证一个起步良好的公司能够成功,一般风险投资家在投资的同时,还要为公司寻找一位专业的CEO,就是这个目的。
真正具备这些条件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一个初创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还要看外部环境好不好,配套条件是否具备。起步太早,条件不具备,事情自然做不成;而行动得太晚,市场已经太拥挤了,机会也就丧失了。爱迪生和福特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合作开发了电动车的原型,但是以当时的配套技术根本不可能造出电动车,于是这件事就没有下文了。但是,如果等到今天所有人都看出电动汽车是未来方向了,再来造电动汽车,也几乎可以肯定难以成功。2000年硅谷成功融资的小公司,几乎无一例外都破产了,因为它们赶上了随后的互联网泡沫破碎。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创业者必须有好运气。这也是NetScreen的共同创始人邓锋和柯严告诉我的,创业成功的关键是要有运气。
一个初创公司,经过多年的努力,解决了上述所有问题,非常幸运地成功上市了,也未见得能发财。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股票能大涨的只有2%一3%,这些年因为上市困难一点,大约有5%的公司在上市后几年内股票大涨,其余公司股市表现平平,甚至不如发行价(即中国常说的原始股价)。远的不说,2011—2012年上市的一些明星公司,包括Facebook、著名社区游戏公司Zynga和最早的团购公司Groupon,上市后不久股价就很快跌掉大半,见表13.2。它们之中只有Facebook后来创了股价的新高,其余公司则再也没有回到IPO时的高度。到今天,依然破发(中国股民对跌破发行价的称谓)的著名企业还有推特、Snapchat等,甚至还包括中国主权基金投资支持的著名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黑石公司。此外,即便公司创始人能挣到一些钱,很多早期员工其实也发不了大财,普通员工只是挣一份辛苦钱而已。
而很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很长时间里股价都不到上市时的一半,包括2005年上市的中国明星半导体公司中星微电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的市值还没有账上的现金多;而中国另一家明星半导体公司展讯也一度跌了90%以上。由于它们都接受了很多来自政府的投资,又不能轻易私有化,便只能年年亏损硬撑着,直到撑不住等人来接盘为止。另一家2013年上市的中国跨境电商公司,上市至今股价跌掉了90%多,市值只有区区4000多万美元,其中账面上还有3000万美元现金,也就是说,公司本身价值只有1000万美元,还不如中国许多只有两三人的创业团队估值高。有人觉得美国股市低估了这些中概公司的价值,其实,高度市场化的美国才真实反映了这些公司的实际情况。
创业的过程本身异乎寻常地艰辛,即倬最后成功了,回首起来也是险情不断。YouTube的两位创始人说,他们在前一家公司挣到了不小的一笔钱,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很快,两人上百万美元的积蓄就烧光了,他们艰难到需要用信用卡购买设备,每个月勉强还出信用卡的利息。他们的运气很好,这时得到了红杉资本几千万美元的投资,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又烧得差不多了。好在当时Google 和微软不惜成本地相互竞争,倬他们渔翁得利,以一个很好的价钱(十几亿美元)被其中一家收购。可是后来回想起,成败就在一线之间。
既然在硅谷成功不易,那么大量的失败者怎么办?通常只有三个出路,找工作或离开硅谷,当然有些没有输光本钱的还可以重新再来。但是,对于那些失败的公司和个人,大家并不关心,甚至没人知道它们和他们存在过。即使很多曾经辉煌过的公司,像网景公司、SGI公司、太阳公司,也会很快被人遗忘。当人们羡慕苹果、Google、英特尔和思科的成功,津津乐道讲述它们的传奇故事时,也应该清楚那是以无数失败者做分母为代价的。
唐代诗人曹松有句中国人人皆知的诗——“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这用来形容硅谷成功的公司,也非常恰当。因为那些光鲜亮丽的公司的背后是无数工程师、产品经理和行政人员付出的血和汗。
3 嗜血的地方
读者也许会觉得我用的标题过于夸张恐怖,但事实的确如此。
在硅谷,首先是工作时间超长。我第一次去硅谷的IBM Almaden研究中心时,接待我的一位科学家在陪我吃完晚饭八点多以后,又回到实验室干活去了。在那之前,我刚访问过IBM在纽约的沃森实验室,记得那里晚上是没有人上班的。于是我颇为惊讶地问他,今天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必须完成。他告诉我,他几乎天天如此。虽然同样是IBM的雇员,在加州一个人的实际工作量,顶得上美国东部两个人的工作量。后来我才知道,加州那些小公司的员工比IBM雇员的工作时间还要长,负荷还要重。我的同学兼同事,一位曾经在华盛顿州雷德蒙德市微软总部和硅谷Google总部都工作过的语音科学家讲,他在Google每周的工作时间是在微软时的两倍。
美国的公司从理论上讲不鼓励加班,从法律上说也不能要求正式雇员加班。对于按小时付薪水的合同工,加班要给加班费。但是,正式员工要是自愿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我不能确定全美国IT行业的员工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也许是40小时左右吧,因为法律规定如此。在美国东部和南部,IT行业从业者的工作时间很少超过这个数字。但是在加州,绝大部分科技公司的员工每周工作时间都远不止40小时。即使是在我们前几章提到过的一些大跨国公司,很多人经常周末要去加班。在小公司里,尤其是还没有上市的小公司,大家每周工作七八十小时甚至100小时是很平常的事。中国一些创业公司的上班时间是所谓的“996”,即每天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上班,每周六天,这就被认为是工作强度大了,但是这样一周其实也不过70小时左右。日本人号称工作时间长,但和硅谷的上班族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更何况在日本,许多人是没事做耗着不回家,而硅谷大家是有干不完的活。易然硅谷工程师的薪水比美国同行要多20%左右,其实每小时实际收人要低得多。更何况,一天只有24小时,工作时间太长,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少了,生活质量就下降了。我在微博里曾经给大家描述过我在Google早期的工作方式:
我一般会在吃完晚饭后把代码修改的清单(Change List)发给克雷格做代码审核,他一般晚上10点左右会回复我,给出修改意见,详细到某一行多了一个空格。我改好后会在凌晨零点前再次发送给他,凌晨2点左右我们俩就所有的细节达成一致并且修改完毕,我会提交代码。一般我直接回去睡觉,而克雷格会干得更晚些。
从这个角度讲,硅谷不是生活的乐土。这倒不是雇主不想对员工更好些,事实上加州的法律比其他州更倾向于保护雇员的利益,但是公司之间的竞争更激烈。所有人,上至公司高管,下至普通员工,在这样的紧张环境下都不得不加班加点地工作。
当然,如果只是工作时间长一些,还可以忍受。硅谷失业的压力要比美国其他地区大得多。到了经济不好的年头,这里的失业率会率先攀升上去。记得网络泡沫破碎后的两年,在硅谷中心的圣塔克拉拉县(惠普、Google、英特尔、苹果、雅虎、eBay、微软、太阳等公司都在该县),失业率高达7%,远高于全国5%的平均水平,这还只是有资格领救济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即拿绿卡的),并不包括很多持有H1B工作签证的人。很多人一年以上找不到工作,被迫离开硅谷,有的去了美国东部,很多移民只能回国寻找机会。中国海归的高潮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很多人为了不荒废自己的技术,宁可不要工资工作(在硅谷,招人的公司发现一个申请者半年以上没有工作,就会很不愿意雇佣这些人,因为公司会觉得这个申请者要么技术已经荒废,要么自身条件不强,否则为什么半年还找不到工作)。我的一个朋友在2002年创立了一个小公司,打出招人的广告,讲明是没有工资的(当然,用了一个好听的说法叫“合伙创业”,可以得到一些可能有价值也可能一文不值的股票)。短短几天里竟然收到上百份简历,其中很多是水平超出要求的工程师。即使有工作的人,也会担心什么时候裁员裁到自己头上。很多时候,不是个人能力问题,而是整个部门被裁掉甚至整家公司关门。覆巢之下无完卵。
在美国东部主要城市,娱乐、文化生活丰富,而硅谷基本上就是文化的沙漠。硅谷人最常去的解压度假场所就只有附近的塔霍湖(Lake Tahoe)滑雪场、里诺(Reno)和拉斯维加斯的赌馆。
由于生活所迫,硅谷的人在外人眼里都相对急功近利和唯利是图。在硅谷,不提供股票期权的公司,几乎找不到技术人员。按规定,一个雇员工作满一年就能按期权价格买下股票(这个过程叫行权,Exercise),因此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在某公司工作满一年,拿到股票期权立刻走人,再到第二家、第三家公司。如果说风险投资是通过分散投资来降低成本,那么很多硅谷雇员则是分散他们的生命来期望有朝一日在一家公司能中上硅谷彩券。在硅谷,一两年换一份工作也很正常,员工也就没有忠诚度可言。这不是个人的问题和错误,而是生活压力倬然。
硅谷就是这样一个“嗜血”的地方。坦率地讲,硅谷的生活质量达不到美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几十年来无数的年轻人把硅谷当作开拓自己事业的首选地,这里有更多机会和梦想。
4 机会均等
硅谷能成为科技之都,而目长盛不衰,必有它的高明之处。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保证机会均等。任何人、任何国家和制度都无法保证我们的社会绝对公平(事实上也没有必要追求绝对公平),但是,一个好的制度要保证每个人有均等的机会。
硅谷是一个到处可见权威的地方。这里不仅有像约翰·亨尼西那样的科技界泰斗、拉里·埃里森和埃里克·施密特那样出类拔萃的工业界领袖,还有被称为风投之王的约翰·杜尔和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红杉资本的合伙人)。这里集中了近百名诺贝尔奖、图灵奖和香农奖得主。各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多如牛毛。如果你开车在路上抛锚了,停下来帮助你的好心人可能就是一个大人物。Google过去主管工程的第一副总裁阿兰·尤斯塔斯就在路边帮助过他人。
但是,硅谷却从不迷信权威。任何人要想在这里获得成功,都得真刀真枪拿出真本事干出个样子。在美国很多地方,尤其是传统产业中,普遍看重甚至过于看重个人的经历而不是做事情的本领。比如一个毕业生要想到位于美国东部的IBM沃森实验室或以前的贝尔实验室搞研究,必须出身于有些名望的实验室,有导师和教授们的推荐(在日本公司更是如此)。大公司雇用一个主管或资深职务的员工,首先要看简历上的经历和头衔。这种做法当然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即使再真实的简历,也不免有夸大其辞的部分,更何况简历上的经历只能证明一个人以前做过什么,而不是今后能做什么。在硅谷谋职,简历固然重要,但是个人的本事(包括和人打交道的软技能)才是各家公司真正看中的。由于每家公司产品的压力很大,同行业公司之间的淘汰率很高,硅谷的公司需要的不是指手画脚的权威,而是脚踏实地做事的实干家。硅谷几十年发展经验证明,那些初出茅庐但踏实能干的年轻人,可能比一个经验丰富但已眼高手低的权威对公司更有用。我们在本章一开始介绍的那些诞生于硅谷地区,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大都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完成的。很多人向我抱怨过Google在招人时忽视以前的工作经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和大部分的硅谷公司一样,Google更相信自己通过面试得到的判断,而不是简历和推荐信,因此招人时总喜欢考一考。不管面试者名气多大,水平多高,过不了考试也是白搭。我有个在美国顶级的计算机系当教授的同学,先推荐了他的一个学生来Google应聘,结果录用了。后来他自己来,Google要考他学生做过的类似题目,他反而没有通过,易然我们很为他感到可惜,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位教授很不服气,对我讲,我的学生远不如我,你们却要了,我发表过那么多论文,拿到过那么多经费你们却不要,说明你们的眼光有问题。我承认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不能为一个人坏了规矩。从Google和eBay及无数硅谷公司成功的经验看,这种不迷信权威、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的做法总体上是对的。它确实有时候会让公司和一位称职的权威失之交臂,但是硅谷的公司也因此能吸收到更多新鲜血液,充满活力。
不仅公司不迷信权威,硅谷的个人也是如此。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很少会因为IBM或斯坦福的专家说了该怎么做就循规蹈矩,而是会不断挑战传统,寻找新的办法。在公司内部,职位高的人不能以权压人,而必须以理服人。在Google、苹果这类公司当老板并不容易,因为一旦知识老化或业绩不佳,就不得不离开。在硅谷各公司内部,易然也有职级之分,但是等级不像传统企业那么明显。更重要的是,公司内部的升迁和毕业学校、学历、工龄长短的关系并不大。因此,硅谷常常有一个怪现象一一你的下属可能会在一两年后成为你的老板。后来担任过微软高级副总裁的陆奇,在雅虎就经常被提拔成为他老板的老板。我在Google的同事科恩是Naunce的创始人,小王在Naunce时是他手下职级不算高的工程师,两个人先后到了Google,小王因为在云计算方面贡献巨大,仅仅三四年职级就超过了科恩。这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做法倬得硅谷公司在全世界更有竞争力。
对创业这件事,创业者的资历固然重要,但就重要性而言远排不进前几位。名气大、职位高的创业者虽然经验丰富,人脉广,但是如果闯劲远不如初出茅庐的牛犊那么足,成功率可能反而低。在风险投资人看来,一个人的经历和身上的光环只能代表过去,而过多财富和曾经有过的地位有时反而会成为创业的负担。事实上,除了甲骨文和英特尔是IT老兵创办的,硅谷大部分著名的公司,如思科、苹果、雅虎、Google、Facebook和优步,包括中国人创办的NetScreen和WebEx,都是由原来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办成的。
自古英雄出少年,这是风险投资家们普遍承认的事实。我在正式做风险投资之前,向红杉资本等很多风险投资机构内的老兵们了解他们投资的一些原则,其中有一条就是创业者一定要有饥渴感。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很难想象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会比一个急于脱离贫困现状的年轻人更有欲望把公司办好。前者办公司常常是为人生锦上添花,而后者则是破釜沉舟,没有退路的。这就是乔布斯勉励年轻人要保持饥渴感(Stay Hungry, Stay Foolish)的原因。因此,资深创业者和年轻人在创业上各有优势,但是硅谷会给予他们均等的机会。这也是很多人虽然知道在硅谷工作艰苦,却愿意留下的原因一一可以获得其他论资排辈的地方所不能给予的机会。
机会均等的另一方面表现在行行出状元。160多年前旧金山是淘金者的天下,一位叫李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的德国人也从纽约跑到这里来淘金。来了以后他发现淘金的人已经过剩了,于是他捡起了他原来布料商和裁缝的老本行,用做帐篷的帆布为淘金者制作结实的工作服,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名的Levi’s牛仔裤。100多年过去了,当年淘金者的踪迹已经找不到了,而Levi’s牛仔裤今天仍然风靡全球。
今天,大家进入IT行业挖金矿时,也和老一辈开拓者一样,真正靠当工程师发财的人只占大约1/4左右,剩下的机会留给了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在硅谷这一片年轻的土地上,只要肯干,大家都有成功的机会。
硅谷地区公司众多,而目每天都有新公司诞生,现有的公司被并购,老的公司关门,因此对法务的需求就特别强。在硅谷的中心城市帕罗阿图,人口只有6万人,从业的律师却有3000人左右,美国很多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在那里都有分支机构,比如比尔·盖茨父亲的KL Gates律师事务所。众多初创公司可能开业不久就关门了,可是那些律师事务所则总是有生意做。
在硅谷“淘金”,总会不断产生科技新贵,于是就出现了替他们打理财务的生意,今天硅谷地区就成为投资银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除了我们以后要专门提到的风险投资,这里的个人财产管理(Private Wealth Management)和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业务也很发达。比如著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有超过10%的个人财产管理经理人都在硅谷,使其在硅谷的分部成为全球仅次于其纽约总部的第二大分公司。由于硅谷房价很高,房屋交易金额大,而且硅谷人口流动性大,房屋交易数量多,因而造就出一大批房地产中介商,其中干得出色的,收人比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要多得多。据著名房地产中介商比尔·戈曼(Bill Gorman)介绍,他十几年里一共交易了价值10亿美元的房产。按照美国标准的3%的佣金计算,他的累计收人高达3000万美元,超过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总。有趣的是,很多金融和房地产业从业者是IT出身的工程师。他们发现硅谷的IT行业已经人满为患,改行去从事其他工作,反而比原来当工程师甚至公司主管要成功得多。
即便不在金融和房地产这类高利润的行业工作,只要努力,一样能事业成功。我们不妨看看这样两个例子。我的一位朋友刚刚装修完新家,替他装地板的是一位华裔老板。这位老板没读过大学,中学毕业就给别人打工当学徒,但是他很爱钻研,又非常勤快,很快就成为装地板的行家里手。几年后自己出来单干,开始接一些小活儿。他要价不高,活儿又做得不错,很快活就多得做不过来了,于是他雇了一些工人,业务便发展起来了。他通过高薪(和IT从业人员差不多)招技术熟练的地板工,所以一直质量很好。慢慢地,开始接到大公司的合同,事业发展很快。即倬在现在美国房地产不景气,很多装修公司没有生意,他手上的合同仍然多得做不过来。第二个例子是我家园丁,一位墨西哥移民,一开始只是一个人给人除草收拾院子。由于他为人热情,乐于助人(比如经常用自己的卡车替主顾运送大件商品),又守信用,他的雇主们就把他推荐给朋友用。很快他就忙得接不了新的主顾了,于是请胞弟过来帮忙,两个人除了替人除草收拾院子,便开始做一些简单的房屋修缮和庭院规划(Landscaping)工作。渐渐地,他就积累起一些财富,雇了一些帮手,开了一个庭院规划的小公司。在房价很高的硅谷,也买上了房子,实现了他的美国梦。
相反,如果一个人不能脚踏实地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即便名气再大,才高八斗,在硅谷也很难混下去。大多数时候,硅谷公司需要的是有真才实干的人,而不太看重那些不能带来实际效益的名气。2000年,由于互联网泡沫导致硅谷过度繁荣,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招不到人,那时找工作很大程度上仅凭一张嘴。很多频繁跳槽而不脚踏实地做事的人跳来跳去跳到一个主管的位置。2001年以后,用人不当的公司很多倒闭或被迫大量裁员,真正的高手,或者还待在原来的公司,或者被别的公司录用,或者转到了学术界。而一大群各个级别的混混都到了“人才市场”上待价而沽。这些人中很多原本是技术精英和管理人才,但是一旦养尊处优时间长了,名不副实了,便很难再在硅谷生存。偶尔会有一两个小公司到那里去找人做事,常常一下子围上一大堆人。如果问他们会做什么,大部分人的回答都差不多,“如果你给我一个团队,我一定能替你管好。”这里面虽然不乏真正的管理者,但是很多都是眼高手低。招人的公司显然不傻,它们需要的是干活的人,而不是给人养老。
相比世界其他地方,硅谷不仅机会多,而目相对来讲最均等的。尽管这里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对失败者很残酷,但还是不断有人愿意来。近年来(2014一2018),硅谷地区每年大约有5000人净流出到美国各州,但是却又从世界各国各地区净流人1.7万——1.8万人,而目大部分是年轻的专业人士。因此,只看到很多人在硅谷地区待不下去而搬到美国其他地区,就得出硅谷竞争力在下降的结论,显然是片面的,硅谷的机制依然在吸引全世界的英才前来这里。
5 硅含量降低
硅谷因半导体而得名,但是今天这里硅的含量并不高,因为这里半导体以外的产业远比半导体产业规模大得多。
硅谷地区硅含量最高的年代是上个世纪60年代。继仙童之后,旧金山湾区的半导体公司可谓是遍地开花,除了在行业内鼎鼎大名的国家半导体、英特尔、AMD、Maxim等公司,还有无数不知名的中小半导体企业。半导体产业的繁荣导致了硅谷地区生活成本的剧增,当时仙童公司的诺伊斯出于竞争的考虑,将部分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生产线转移到了香港。事实上,香港是全世界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能够制造集成电路的地区。此后,硅谷地区一方面有新的半导体公司诞生,现有的公司有的还在扩大规模,但是同时半导体工业也在向外转移,它只是在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计算机系统和软件产业的发展让硅谷地区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从那时到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硅谷著名的大公司有:惠普、英特尔、太阳、SGI、IBM(Almaden实验室)、甲骨文、苹果、3Com、希捷(Seagate)、AMD、国家半导体(National Semiconductor)、思科和基因泰克,等等。虽然其中大部分都是所谓的硬件公司,硅的含量依然很高,但是单纯的半导体公司比例不到一半了。这表明硅谷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第一次产业转型和升级。
90年代以后,虽然硅谷的半导体业还在发展,新的半导体公司还在诞生,比如著名的英伟达公司就诞生于那个时代。但是,半导体在硅谷经济中的比重已经大大下降了。在2001年新世纪开始的时候,硅谷最大的公司是思科、惠普、英特尔、基因泰克、eBay、雅虎、甲骨文、Google、IBM和苹果。其中Google、雅虎和eBay是互联网公司,IBM将存储设备部门卖给了日立公司后,和甲骨文一样都是软件和服务,而基因泰克干脆就不是IT科技公司,而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制药公司。这些公司的硅含量近乎为零。即倬是英特尔,也已经将其工厂迁到美国其他州及海外了,它甚至逐步将低端研发部门迁到费用低廉的亚利桑那和俄勒冈。虽然在新世纪里,半导体在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分量仍然在增加,但是硅谷却被人们称为是遗存工业(Legacy Industry)。今天,硅谷最知名的产业是互联网和通信,离半导体更远了,在不知不觉中又完成了一次产业的升级转型。
造成硅谷半导体业衰退的直接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反摩尔定律的效应。由于半导体的价格每18个月降一半,一家公司研制出一款新的芯片以后,它不能指望像制药公司那样随着销量的上升而利润不断增加,过不了多久,这款芯片的利润就薄得必须将其淘汰了。整个半导体工业天天都在为利润率发愁。从这个角度来说,半导体工业很难在费用高昂的硅谷长期发展。我们前面提到,硅谷是一个拒绝平庸的地方,当一个行业的利润率无法维持硅谷高昂的费用时,它就必须搬出硅谷。相比之下,软件产业则不受反摩尔定律的影响,可以维持很高的利润率,因此得以在硅谷快速发展。
其次是“亚洲制造”效应,由于硅谷靠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起飞,在上个世纪70年代它便聚集了很多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的专家和工程师。同时,也促进了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大电机工程系的发展。这些人,包括从仙童离开的,也包括斯坦福和伯克利的教授和学生,开始了第二轮的半导体公司和计算机硬件公司的创业。其中的代表者包括设计和制造RISC处理器的MIPS公司、太阳公司和SGI公司,以及后来的思科、英伟达、美满电子(Marvell)和Atheros。和上一代半导体公司大多是由美国人所创办的不同,新一代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公司,很多都是由亚裔创办,或由亚裔担任高管。其中英伟达、美满电子和Atheros都是由华裔学者和企业家创办的。第二代半导体和计算机公司从一诞生开始,就没打算自己从事半导体和硬件制造,他们制作设计,然后拿到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后来是中国大陆)去生产。再到后来,很多低端的设计工作也放到亚洲去完成了,硅谷的硅含量自然就越来越低了。
世界上很多城市会因为一个产业而兴起,比如德国的鲁尔兴起于采煤和炼钢、美国的匹兹堡和底特律分别靠钢铁业和汽车业发达,但是,随着这些工业的饱和和衰落,相应的城市也渐渐衰落了。硅谷兴起于半导体工业,因此很多以老眼光看待硅谷的人总是觉得当半导体工业不断从硅谷外移之后,它早晚有一天会步匹兹堡和底特律的后尘。可是,50多年过去了,产业的变革不仅没有让硅谷衰退,反而让它变得更加繁荣、更有竞争力了。
讲述完硅谷的这些与众不同之处,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它不断繁荣的秘诀了。
6 真正的奥秘
如果说硅并不是硅谷真正的特征,那么什么才是呢?很多人觉得是创新,但创新是结果不是原因,因为没有哪个地区不想创新,但是要做到创新并不容易。我们在第3章讲到,硅谷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仙童公司,它既是叛逆的结果,也在鼓励着新的叛逆。事实上,叛逆是硅谷最明显的特征,它成为一种文化植根于硅谷的基因。硅谷通过对传统的不断颠覆,维持着它的活力。但是,硅谷的叛逆者们所做的是有节制的颠覆行为,他们更多地显示出建设而不是破坏的特点。
6.1 会建设的颠覆者
6.2 对叛逆和失败的宽容
6.3 多元文化
只要在硅谷地区生活一段时间,就能体会到这里的多元文化。1996年,我初到美国时,第一站是旧金山湾区,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周,感觉仿佛还在亚洲,抬眼望去到处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亚裔,而目在当地能够让中国人继续享受到很多国内的生活习惯,比如有很多中餐馆和亚洲食品店。当我继续往前旅行,来到美国东部时,才真正体会到自己来到了另一个国度,必须开始过美国人的生活了。不仅是中国人,在硅谷地区生活的很多移民或多或少都会有类似的感受。
硅谷地区的这种特性首先是由人口结构决定的。历史上,这里曾经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主要居民来自墨西哥,后来在淘金热中涌人了从东部来的大量的美国白人,随后在修建西部和泛太平洋铁路期间,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移民到此。硅谷诞生之后,大量来自亚洲和欧洲的移民成为新移民的主体。在过去的70年里,硅谷地区最大的城市圣荷西市的人口从10万增长了10倍,超过了100万。这主要是新移民涌人的结果。今天,易然亚裔仅占美国人口的4%左右,但却占到了硅谷地区的25%。而在苹果总部所在的库帕蒂诺市,亚裔更是占到总人口的2/3左右。
世界各地移民的到来,首先给硅谷地区带来了多元的文化。而多元文化不仅让硅谷公司可以吸取各种文化的精华,设计出技术精品,而目让硅谷公司的产品能够成为全球化的产品。事实上,在硅谷哪怕是一个十几个人的小公司,它所设计的产品也是针对全球市场的,而不仅仅是为了美国市场。我们在第2章“蓝色巨人”表2.2中给出了美国主要科技公司海外营收的占比,这些公司要么总部在硅谷,要么有很大部分的研发团队在硅谷地区。相比之下,除了华为和联想,绝大多数中国高科技企业在海外的收人近乎为零。
我们在后面的第20章中介绍了社交媒体公司WhatsApp,它的产品相当于国际版的微信。当这家公司还只有十来个工程师的时候,就支持了20多种语言,一半多用户来自海外。在Facebook以近200亿美元的高价收购它之前,腾讯也和WhatsApp谈了收购的可能性,因为腾讯在海外完全无法和这家小公司竞争。在腾讯看来,其产品还有很多颇为基础的功能都没有做,却优先发展全球市场,未免与腾讯的文化格格不人。在腾讯内部,公司最高领导常常亲自试用微信产品,一旦发现什么细小的问题,都会在第一时间通知项目组,即倬是在凌晨也不例外。而中国大部分公司的中层干部和员工,对领导意图的反应速度就不必多说了,因此那些来自上层的工作指令总是排在最高的优先级。当时微信有几百名工程师,但产品国际化的工作相比之下则很难得到开发人员的重视。时间一长,这个很有前途的即时通讯产品就被过度优化成只适合中国人倬用的特定产品了。比如微信直到2015年之前的各版本,删除单独一条聊天记录的功能并不显眼,一般用户找不到,这或许跟国内用户很少倬用这个功能有关,而在世界其他地区这个功能却很重要。WhatsApp的这一删除功能,其实是照着Google Gmail的倬用习惯设计的,因为全世界的用户都被Google训练成像那样去倬用删除键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Gmail在中国没多少人使用,主要由中国人构成的微信团队完全不知道中国以外的互联网用户的这一习惯。如果微信当年是一个国际化团队,也就不需要等到2015年才做出符合全球用户习惯的删除键。今天,易然微信在这个功能上与国际接轨了,但产品总体来讲依然是照顾中国用户的习惯。
在硅谷的很多公司,明确规定产品和服务要在世界各国同步推出,而不是仅仅照顾美国。在Google,任何产品和服务在推出英语版本的6个月内,必须开发出支持主要亚洲语言和欧洲语言的国际版。当然,有人可能会问,6个月做不出来怎么办?答案很简单:推迟英语版的面世时间,抓紧时间先开发国际版。相比之下,很少有中国企业这样做事情。
在英语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单词缩写,一个是i18n,另一个是l10n,它们分别代表internationalization和localization,这两个词写起来太长,因此产品经理们偷懒,取internationalization的第一个字母i和最后一个字母n,中间用18表示在i和n之间还有18个字母,用i18n代表国际化。类似地,创造出l10n代表本地化。国际化和本地化的差别很大,中国很多企业往往会混淆这两个概念。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有着不同的习惯,适合一个地区的产品未必适合其他地区,因此,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做全球化的市场就是用不同的产品(设计或方法)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这其实是本地化,不是国际化。这两种不同的思路在开拓全球市场时,做法完全不同。
以本地化的方式进入全球市场,在开发产品时是有明确的地区定位的。中国的大部分公司会先想到中国市场,然后是东南亚等新兴而未饱和的市场,最后才是竞争激烈的欧美市场。这种做法看似稳妥,但是从一个市场进入另一个市场时要进行产品的本地化,每进入一个新市场,就几乎要重新来一遍。更糟糕的是,针对一个市场的改进通常不能直接推广到其他市场,因为在开发本地化产品时,所有的设计相对都是独立的。具体到与IT有关的产品和服务,不同国家和地区使用的软件代码库常常是不同的。这种做法,一开始看似省时间,但是进入海外市场非常困难。
全球化的做法则不同,为了赢得市场,一款产品要充分考虑到全球用户各种可能的需求,并尽可能一次性满足。根据我们在Google的经验,这么做一开始的工作量可能要增加两三倍,但是从一个市场进人另一个市场的成本就会变得非常低。
做一个让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都喜欢的产品并不容易,产品的多元文化属性这时就会变得特别突出。我在《文明之光》中讲述了为什么全世界都喜欢青花瓷,因为它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产物。类似地,今天的iPhone也是如此。虽然每一个iPhone背后都写着加州设计,但是它实际上也是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它的设计者(最后拍板的)乔布斯在产品设计的理念上吸收了东方文化,尤其是禅宗文化的精髓。据乔布斯的朋友、著名建筑师林璎在回忆中讲,乔布斯很好地将日本文化中那种“少即是多”的思想贯穿到了iPhone(和很多苹果产品)的设计中。乔布斯还结识了著名建筑师贝聿明和日本著名的服装设计师三宅一生等人,从他们的作品中吸收到各种文化的精髓。我们可以看到,在iPhone中,没有复杂而花里胡哨的按键和复杂的功能,这样,不需要看使用手册,任何人都能很快学会倬用iPhone。具体到iPhone的工业设计,其主要人员来自德国,因此它也吸收了德国工业设计的精华。今天华为的高端手机在全世界也很受欢迎,从本质上说也是多元文化的产物,这些手机是日本、芬兰、德国、俄罗斯和中国多国开发团队共同开发的成果,这还不包括里面倬用的处理器技术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
硅谷地区易然从主权上说是美国的领土,不过把它看成是全世界在太平洋东岸的一个缩影,或许会更加准确一些。从当年淘金、修铁路到今天建设硅谷,大量外来的优秀移民,其实是在不断地给这个地区输送新鲜血液。相比当地的居民,移民常常更富于冒险精神,否则他们也不会远渡重洋来到这里。因此,红杉资本才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要求投资对象,即初创公司的创始团队中,至少有一个人是第一代移民,以此保证这个公司具有足够的冒险精神和竞争力。
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硅谷其实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仅人员在不断流动,而且产业也在不断变化,那么它有没有不变的地方呢?有的,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内容了。
7 亘古而常青
……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当独立的软件业在计算机产业中脱颖而出时,以甲骨文为代表的硅谷软件公司没有错过那次机会,它们采用了新的商业模式,不仅在与IBM等东部软件公司的竞争中站住了脚,而且实现了超越。
和软件产业同时崛起的还有基于基因技术的生物产业。创办一家生物公司常常要比创办一般的IT公司更难,这主要是因为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U.S.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的限制,使得一项生物科技的发明很难在短时间即几年内变成产品和利润。所以,创办生物公司投入大,周期长。但是,在冒险家乐园的硅谷,仍然有很多人坚韧不拔地在生物科技领域艰苦创业,其中不乏成功者。最典型的就是基因泰克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76年,早期依托于旧金山加大医学院,利用基因技术制造出药用胰岛素,拯救了上千万糖尿病患者的性命。此后,它专门研究和生产Avastin、Rituxan等抗癌药品。今天,基因泰克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药品公司,有一万多名员工,包括无数杰出的科学家,在被瑞士罗氏公司收购之前,基因泰克的市值高达800亿美元,并多次当选全美最佳雇主。
基因泰克的成功经验很值得大书特书,易然我没有把它单独成章,但是这家明星企业值得在这里谈一谈,以便大家了解硅谷的灵魂所在。
在介绍基因泰克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美国医药市场的简单情况,以便更好地理解基因泰克公司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在美国,除了像西洋参和卵磷脂那样的保健品外,药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处方药,比如抗生素;另一类是非处方药,比如治感冒的泰诺。前者利润当然远远高于后者,而其中又以有专利的新药最挣钱。比如基因泰克一共只有十种药品在市场上销售,其中销售额最低的每年也有几亿美元,最高的Avastin年销售额近30亿美元。美国专利法对新药有20年的专利保护期,但是这20年并非是从新药上市后开始算起,而是从它完成研制、申请了主要专利的时间开始算起。在研制完成到上市,中间要进行各种动物实验的临床试验,一般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留给研制新药的厂家最赚钱的时间通常不到十年。任何一种特效药,不论过去多么挣钱,一旦过了专利期,其他厂家有能力仿制时,它的利润就一落千丈了。而新药的研制投人又非常巨大,据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院长米诺博士介绍,今天一款新药的科研投入大约是20亿美元,但是其生产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甚至盗版的成本都很低),在这一点上制药业很像软件业(实际上,世界上药品的盗版甚至比软件盗版更严重)。因此,虽然药品市场没有反摩尔定律限制药品利润,但是专利法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它既在专利有效期内保护发明,又防止个人和公司长期垄断发明,迫使医药公司只有发明了新药才能挣得到钱。如果一家公司旧的支柱药品专利到期了,而新的专利药品还没有跟上来,这家公司的业绩就会一落千丈。2008年,默克公司(Merck,在美国和加拿大之外的地区,又称MSD,即默沙东)就因为旧的处方药专利到期,新药的研发没有跟上,股价急剧下跌。可以说,制药公司的竞争实质上是创新和科研效率的竞争。
照理说,制药业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行业,应该有很多新的公司冒出来才对。但是,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人为造成了这个行业极高的门槛。根据FDA的规定,所有处方药和用于临床的医疗仪器,甚至是治疗方法的临床试验,都必须得到FDA的许可,更不用说在市场上销售了。而这些许可证是极难拿到的,要进行无数对比试验,并目要尽可能了解和降低所有可能的副作用。FDA的初衷很好,毕竟人命关天不能不仔细(历史上,磺胺类消炎药刚进人美国时,因为把关不严,造成了大量患者死亡),但是这也使得小公司几乎无法进人处方新药的市场,它们通常会在适当的时候将公司卖给大药厂。另一方面,传统的大型制药公司,诸如辉瑞(Pfizer)和默克(Merck),自身研发新药的能力常常变得很弱,它们的研究部门很像30多年前的贝尔实验室,一个科学家进去一干就是一辈子。但是,由于这些公司有着高额的垄断利润,并目受到FDA变相的保护,它们在制药业的统治地位是很难被撼动的。
而以创新著称的硅谷却敢于挑战传统。基因泰克公司的崛起,打破了传统制药业平静的水面,创造了一个神话。相比有170余年历史的辉瑞制药(成立于1849年,它的伟哥闻名于世)和一百多年历史的默克,只有30多年历史的基因泰克只能算是小孙子,但是却一直能以每年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发展,而辉瑞制药等公司的业绩基本上停滞不前,营业额时高时低。
基因泰克成功的关键在于创新和专注。和生产上百种药品和保健品的辉瑞公司不同,基因泰克专注于研制和生产少数抗癌特效药,并保证每一种药品的年销售额均在亿元以上。为了防止专利到期致倬利润锐减,基因泰克将销售额的20%(2008年是23亿美元,此后它被罗氏制药收购,不再向美国证监会报告财务情况)投人到新药研制上。因此,它的研发产品线上总是保持着足够数量的新药。在2009年它被罗氏收购之前,它有14种药和治疗方法已经进人了上市前的最后阶段,有15种药和治疗方法进人了研制的第二阶段,13种处于初期阶段。可能有人会觉得十几种药品数量也不算多,要知道人类至今一共才发明了5000种被批准倬用的药品。基因泰克这样的布局,让它的产品线上会源源不断地推出新药,替代专利到期的旧药,成为新的增长点。
创新必须依靠技术实力。和Google一样,基因泰克也是世界上单位办公面积博士密度最高的公司之一。在被罗氏收购之前,它的7名董事中有5名博士,9名执行官中也有6名博士。基因泰克的科学家在同行中是佼佼者,在公司内部地位也很高。在我读过的上百个大公司年度报告中,基因泰克是唯一介绍其所有资深科学家(Staff Scientists)的公司。
当然,技术只是保证公司成功的诸多必要条件之一,但远不充分。像辉瑞这样传统的制药公司,易然赚钱很多(它一度在全世界10个最挣钱的药品中占了4席),每年用于新药的研发经费更高(2008年,辉瑞的研发投人达80亿美元,是基因泰克的近4倍),但是由于体制的问题,它自身的研发效率却是主要医药公司中最低的,只能靠购买小公司获得新药,这样就导致新药的成本上升,开发周期加长。辉瑞等公司的问题在于,易然它们有优秀的科学家,但是因为缺乏股权激励,整个企业人浮于事。而身处硅谷的基因泰克则不同,它完全按照IT公司的模式经营,一方面通过股权激励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不得不面对硅谷地区生活压力,倒逼公司创造出更高的业绩。
基因泰克只是硅谷生物科技成就的一个亮点。今天的硅谷是世界上新兴生物公司最集中的地方。这里拥有两所美国排名前十的医学院一—旧金山加大医学院和斯坦福医学院,以及全世界最好的化学系—一伯克利加大化学系。再加上充足的风投资金,都为创办生物和医药公司创造了条件。当然,硅谷人的创业热情和全新的分配制度才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否则哈佛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周围应该有很多生物公司才对。
当计算机软件和生物制药的浪潮方兴未艾之时,互联网又在硅谷兴起了。我们已经介绍了和互联网有关的思科和雅虎,后面还会介绍Google和eBay,有关互联网的发展这里就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以Google和雅虎代表的互联网公司,颠覆了以微软为代表的软件公司向每一个终端用户(End User)收钱的商业模式。而通过在线广告的收入保证终端用户可以免费享受以前的付费服务。在整个互联网行业里,除了亚马逊,美国主要的互联网公司都在硅谷,包括当今世界上营业额和利润最高的互联网公司Google。
在硅谷,不论是投资者还是创业者,都已经习惯了这种快速的产业变迁,人们不断在寻找着下一个苹果、思科、Google或Facebook,而不是固守现有产业。硅谷的成功,其实是信息时代对工业时代的颠覆,这种颠覆是全方位的,从企业制度、资金来源、利润分配,到人与人的关系,当然,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围绕创新这个亘古不变的主题展开的,这也正是保障硅谷的创造力长盛不衰的原因。
结束语
今天,旧金山附近恐怕已经找不到一块金矿石了,“旧金山”这个名字只能代表它过去的历史。不仅如此,硅谷的含硅量也在不断下降,也许有一天,硅谷也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名称,那时大家会想起半导体工业曾经在这里很繁荣。但是它绝不会像底特律和匹兹堡那样从此衰落下去,而仍然会是世界科技之都,因为硅没有了,而创新留下来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硅谷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硅谷的经济主要是靠科技进步而非泡沫驱动的。今后,硅谷的竞争仍然会很激烈,不断会有旧的公司消亡,旧的产业衰退,又不断会有新的公司创立和成长,新的产业诞生和繁荣。硅谷过去是、今天是、明天还会是年轻人梦开始的地方。
硅谷大事记
1951 斯坦福大学把闲置土地租给惠普、柯达等公司,硅谷的前身斯坦福工业园开始建立。
1957 “八叛徒”在硅谷创立仙童半导体公司,硅谷从此得名,半导体产业在硅谷兴起。
1969 硅谷的SRI研究中心成为早期互联网雏形的四个节点之一。
1972 风险投资公司KPCB在沙丘路成立,风险投资公司从此在硅谷快速发展。
1995 互联网泡沫在硅谷兴起。
2001 互联网泡沫破碎,成千上万的硅谷公司破产,硅谷进人发展低谷。
2003 特斯拉公司在硅谷成立,次年马斯克投资这家公司并担任CEO,2010年该公司上市。
2004 随着Google的上市,硅谷再度繁荣,直到今天。
2008 硅谷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几乎未受影响,Facebook和Twitter等公司带动硅谷进一步往互联网和软件转型。
2012 著名的互联网2.0公司Facebook上市。
2015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打车公司优步(不包含其中国业务)在最新一轮融资中估值625亿美元,不仅成为全球最值钱的(有估值的)未上市科技公司,而目成为美国所有和交通相关的行业中价值最高的公司。
2019 5月,优步在纳斯达克上市,首日破发,市值为700亿美元左右。
第14章 短暂的春秋 与机会失之交臂的公司
1 太阳公司
1.4 拉里·埃里森的诊断
在2008年,金融危机对于亏损频仍的太阳公司更是雪上加霜。到2009年,由于业绩不佳,它的市值比2007年又下跌了一半,终于跌到了对它觊觎已久的甲骨文公司可以收购它的价格。包括太阳公司创始人麦克尼利在内的董事会批准了甲骨文公司的收购提议,经过美国政府,尤其是欧盟马拉松式的反垄断审核,两家公司的并购最终得以批准。欧盟本来一直担心这次并购会对甲骨文在欧洲的主要对手德国SAP公司不利。但又担心太阳公司一旦倒闭,欧洲会有大量人失业,最终还是批准了。这次并购只花了74亿美元,只有太阳公司市值高峰时的3%,而目全部是现金交易,说明甲骨文公司不愿意为此稀释自己的股票。
在PC时代,唯一能和微软的盖茨一争高下的就是甲骨文的埃里森了。埃里森在收购太阳公司前放话,他只要一年时间就能让太阳公司扭亏为盈,而目创造出上亿美元的利润。在收购完成后,埃里森给太阳公司进行了号脉诊断。
埃里森说,太阳公司有很好的技术,很好的工程师,但是他们的管理极其糟糕(Astonishingly bad managers),而且做出了许多错误的决定,所以才让我们以很便宜的价钱收购成功(埃里森的原话是“made some very bad decisions that damaged their business and allowed us to buy them for a bargainprice”)。埃里森认为太阳失败的原因有下面几点。
第一,不关心盈利。销售人员的指标是销售额,而不是利润。销售人员的提成也跟销售额而非利润挂钩。这样,几乎所有的销售人员不是尽可能高价卖出公司的产品,而是尽可能让公司多让利来取悦客户,达成交易。这样虽然看上去每个销售人员都达到了预期,但是卖得越多公司亏得越多。有些时候,销售人员每签一份合同,太阳公司就亏一百万美元。这看上去是一种很荒唐的指导思想,但是在1990年以后的很多跨国公司,包括摩托罗拉、诺基亚和宏碁,都曾经在这种荒唐的指导思想下经营。很多新兴的小公司更是以烧钱为乐,而美其名曰先占市场再盈利,最后的结果是永远不能盈利,直到关门或倒闭。
第二,管理者心不在焉。太阳公司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CEO施瓦茨热衷于写博客,阐述自己的经营思想和太阳的战略,这在IT界是出了名的。埃里森批评他不务正业,“再好的博客都代替不了好的处理器,再好的博客都代替不了好的软件,无论多少博客都代替不了销售。”(Really great blogs do not take the place of great microprocessors. Great blogs do not replace great software. Lots and lots of blogs do not replace lots and lots of sales.)
第三,简单地迎合客户。每当销售人员和客户打交道时,客户总会提出一些需求。这些需求有些是合理的,但是大部分并不合理。遇到这种情况,太阳公司的销售人员总是一味向客户承诺,下一个版本一定会满足客户提出的需求。这种销售策略有两个致命的问题,首先是客户可能倾向于等一段时间购买下一个版本,而不是马上签约。其次,这些需求很多可能是不合理的,剩下的又有很多做不到,因此下一个版本还是不能满足用户提出的需求,这样用户就有受骗的感觉,或是认为太阳公司技术不行。虽然销售人员的初衷是尊重客户,但是最终反而让客户失望。和太阳公司的做法相反,甲骨文公司从来是有什么卖什么,不允许销售人员对用户作任何类似的承诺,以免让用户对以后的版本心存不必要的幻想。
第四,停止那些毫无前途的项目。太阳公司有一个处理器项目开发了很长时间,一直进展缓慢。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处理器的开发进度不能赶上摩尔定律要求的速度,等开发出来就不会有市场了。太阳公司的那个处理器项目就是如此。埃里森说,这个处理器如此之慢,如此耗电,以至于要用一个30厘米(12英寸)的风扇来散热降温,这种没有前途的项目要及早停止。
最后,埃里森认为,太阳公司在甲骨文的领导下,将创造出比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大的成就。埃里森的豪言壮语不是毫无根据的大话,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数据库公司,甲骨文每年都要为客户配很多服务器,原本需要从惠普购进,现在可以直接采用太阳公司的产品了。让埃里森更加庆幸的是,对手惠普公司居然把能干的CEO赫德开除了,甲骨文毫不犹豫地在第一时间将赫德揽人麾下。作为深知惠普底细和战略的赫德,成为了甲骨文公司和惠普竞争中的王牌。
被合并后的太阳公司,砍掉了很多琐碎低效的项目,在甲骨文的羽翼下不仅生存下来,甚至还能开始挑战IBM和惠普公司了。甲骨文和太阳公司的共同王牌是,它们能将服务器硬件和数据库软件的整体性能优化得非常好。以前硬件厂商(比如服务器公司)和软件厂商(比如数据库公司)易然都在努力改进自己产品的性能,但是局部的优化拼凑到一起,整体上未必能取得最佳效果。在此之前只有IBM同时拥有软硬件两部分,甲骨文在竞争中多少吃点亏。因此,拥有自己的硬件是甲骨文长期的梦想。现在,它可以全面发挥软硬件上的优势,跟IBM一争高下。基于太阳服务器优化的甲骨文系统很快就面世了,甲骨文在广告里宣传其产品的性能是IBM同类产品的六倍。到2011年,甲骨文在服务器系统和数据库软件上的市场份额都有稳定的增长。但是无论如何,太阳公司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公司了。
太阳公司大事记
1982 太阳公司成立。
1986 太阳公司上市。
1995 太阳公司推出著名的Java程序语言。
2001 “9·11”事件以前,太阳公司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此后,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碎,它的市值在一个月内跌幅超过90%。
2004 太阳公司和微软在旷日持久的Java官司中和解,后者向前者支付高达10亿美元的补偿费。
2006 共同创始人麦克尼利辞去CEO一职,施瓦茨担任CEO后尝试将太阳公司从设备公司向软件服务型公司转型,但未获成功。
2010 太阳公司被甲骨文公司收购。
2 Novell公司
要谈Novell公司,不可避免地要先介绍3Com公司。
在微机出现的前几年,用户大多是孤立用户一一彼此的计算机互不通信。微机一般只是为了满足个人娱乐(比如游戏)、学习、文字处理、日常管理和简单的工业控制等需求。在金融企业中(比如银行)倬用的联网的计算机系统几乎无一例外是由中央主机(Mainframe)加外围终端构成的——所有计算都是由中央主机完成,而外围终端不过是输入和显示设备。中央主机采用分时的操作系统,同时为众多终端用户服务。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以前,没有人打算用微机取代大型计算机系统。
但是,就在1979年,发生了一件当时没有引起人们关注,但对今后计算机发展有深远影响的事。那一年,施乐公司举世闻名的帕洛阿尔托实验室里几位发明了以太网(Ethernet)的科学家创办了3Com公司,开发出以太网的适配器(Adaptor),俗称网卡。易然3Com最早是为IBM和DEC等公司的大小型中央主机设计网络适配器的,但是,随着微机的普及,3Com公司很快就将生意扩展到微机领域。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IBM-PC/AT及其兼容机在很多任务中已经能取代原DEC的PDP和VAX等小型机,而目微机的性价比要高一个数量级以上。如果能将微机联网,共享数据和硬件资源,它们就可以取代小型机系统。遗憾的是,微机最初设计时根本没有考虑资源共享,网络功能为零。3Com公司的以太网服务器和适配器弥补了微机的这个不足,解决了微机的联网问题。以前的VAX或惠普小型机系统采用如图14.4所示的架构。
图14.4 小型机系统架构
资源和数据是集中管理的,所有的计算、存储和打印由小型机完成。它的好处在于信息是共享的,但是成本非常高,一个几十人的小型企业,基本上用不起VAX小型机加终端的计算机系统。我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20一40个用户的VAX系统需要花费近200万人民币。除了硬件的投入,小型机系统还需要专门的机房和管理人员,这些管理人员必须经过硬件公司的培训。易然小型机速度不慢,但是它的计算速度摊到每个用户上并不快。小型机是整个系统的中心,它一出问题,整个系统都无法工作。微机联网后,在很多时候可以代替小型机,它的架构如图14.5所示。
图14.5 微机联网架构
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微机局域网(PC LAN)的系统中,有一台网络服务器,它通常是一台高性能的微机,当然也可以是小型机和工作站,主要用来管理网络和存储共享的数据,并作为桥梁在微机之间交换数据。计算基本上是在微机上完成,部分不便共享的文件也可以保存在本地微机上。由于每台微机都可以独立运作,网络服务器即使出了问题,微机也可以单机工作。易然每台微机不如小型机快,但几十台微机总的计算能力超过小型机。而目,能够完成同样功能的系统,微机局域网相比之下要便宜得多,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这样一个管理40台微机的系统硬件投人只需六七十万元人民币。而且,微机系统不需要专门的管理员,运营成本也低。总的来说,相比小型机,这种基于微机局域网的计算机系统,在大多数应用中优点多于缺点。所以,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起,微机局域网代替小型机系统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也是DEC后来被康柏收购的原因)。
3Com公司虽然搞出了微机局域网,但是该公司目标不明确,从网络适配器、网络服务器到网络操作系统,什么都做。这也许是因为它创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时IT行业最挣钱的还是硬件,所以3Com公司实际上是以硬件为主,软件为辅。即使它在网络上失败以后,它仍然习惯性地以硬件为主,买下了生产掌上个人助理系统Palm Pilot的母公司U.S. Robotics。由于以太网的标准是公开的,它的适配器没有什么高技术,谁都可以做。而以太网的网络服务器实际上就是一个高端PC,任何PC厂商都可以做,因此,在3Com公司出现后,各种兼容的网卡和网络服务器就出现了,这个时候微机局域网市场像微机市场一样混乱而且竞争激烈。其实,微机局域网中最关键的技术是网络操作系统。在这个方面也需要一个类似微软的公司来统一,Novell公司便应运而生了。
Novell公司也是诞生于1979年,但它成为网络公司并目改名为Novell是1983年的事,这时,3Com已经是局域网方面的大哥大了。Novell公司进人网络领域后目标一直很明确一—专攻操作系统。如果说3Com在微机局域网领域的地位有点像苹果在个人电脑领域中的地位,那么可以把Novell对应于微软。
Novell公司搞了一个叫NOS(Network Operating System)的操作系统,对应于微软的DOS。它采用和微软MS-DOS同源的DR-DOS,因此它的网络操作系统实际上可以完全独立于微软的操作系统运行,同时又和微软的DOS兼容。虽然Novell后来买了一家网卡公司也做点硬件,但精力一直放在网络操作系统上。随着Novell的网络操作系统在微机局域网上越来越流行,它处在了一个和微软同样有利的位置:不管用户使用哪种品牌的PC和网络硬件,都可以倬用Novell的操作系统。Novell网络操作系统不仅安装十分容易,而目搭建一个局域网也简单到非专业人员看看说明书就可以搞定。一个没学过计算机的人看着别人干两次就会了。读者如果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中关村转过一两圈,就能记起当时任何一家两三人的小公司都会在自己的业务上写上“网络安装”等字样。很快,Novell的操作系统在局域网上就像DOS在PC上一样普及。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Novell公司成长得一帆风顺,很快超过了3Com公司,到1990年,它几乎垄断了整个微机局域网操作系统的市场,营业额接近微软(9亿美元对微软的11亿美元)。因为微机联网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而目微机的局域网比基于UNIX服务器、工作站和TCP/IP协议的网络在中小企业中更有前途,Novell公司很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微软一一它可能垄断企业级的操作系统。在接下来的5年中,Novell仍然靠着浪潮的惯性,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到1995年。那一年Novell的营业额超过20亿美元,相当于微软同年40%的水平。现在回过头来看,Novell这5年的业务易然不断增长,但是,它的进步还是远远落后于微软。
2.2 操作系统之败
显然,微软不可能看着Novell做大,但是,直到1994年以前,它们的竞争并不引人注意。由于微软当时的核心业务还是以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为主,它和Novell的业务不太重合,两者之间的共同利益甚至大于矛盾。在当时,一家企业在安装网络时有两个主要选择,基于各种版本的UNIX和TCP/IP协议的局域网,或者基于Novell的NOS的局域网。前者在用户看来是UNIX,后者是DOS。虽然Novell采用的是DR-DOS,但是用户倬用起来和微软的MS-DOS一模一样,对程序开发者来讲也是一样。Novell无疑是在帮助微软和UNIX争夺企业级的市场。当时,微软在网络操作系统上毫无可圈点之处,它甚至临时选择了IBM的OS/2 LAN Server来抵消Novell在网络上的优势,但是OS/2 LAN Server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一种主流的网络操作系统。
1993年和1994年,正如日中天的Novell进行了两次对公司业务颇有影响的并购。第一次是从AT&T购买了UNIX的版权,显示Novell进军UNIX企业市场的决心,从那以后,Novell的网络操作系统有了服务于UNIX工作站的版本。但是,Novell没有直接推广UNIX,说明Novell的技术路线方向明确,并没有像一些失败的公司那样左右摇摆;第二件事是收购被微软打垮的字处理软件WordPerfect,以及Borland公司的一个制表软件,表明了Novell进军办公软件市场的决心。后一次收购后来一直有争议,很多人认为Novell不务正业(网络操作系统),胡乱扩张,导致它在网络操作系统上失去了对微软的优势。我个人倒觉得Novell的做法并没有大错。当年,Novell在微机局域网操作系统市场上已经占了百分之七十几的份额,按照诺威格宿命的观点,Novell不可能再让市场占有率翻番了,必须开拓新的增长点。从企业级操作系统进入企业级办公软件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事实上,微软的Office办公软件从企业中挣的钱一直比从个人用户身上挣的钱多,这证明Novell的切人点是对的。今天的Google也是由在线服务进而进人在线办公软件市场的。只是,当微软有了字处理软件Word和制表软件Excel以后,市场上很难再容纳第二家办公软件。不仅是Novell,太阳公司和IBM都试图进人企业的办公软件市场,但都被微软挡在了门外。
从1995年起,微软和Novell之争起了质的变化。微软一年前推出的Windows NT对Novell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了。用户已经从DOS转向了Windows,Novell的操作系统相对微软的Windows NT几乎没有优势可言。
很难想象一个局域网会在其网络服务器上安装Novell的操作系统,同时在联网的微机上倬用Windows。显然从服务器到微机一律采用微软的Windows是更好的办法,这时胜利的天平开始向微软倾斜,并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1995年以后,Novell仍然不断在提升自己的产品,并且在技术上做得很好。它的网络操作系统支持所有主要的计算机(运行Windows的PC、UNIX工作站和苹果的电脑,以及IBM的大型机),为采用多个厂家计算机的复杂的网络系统提供了高性能的统一平台。Novell的操作系统既可以用专用服务器,也可以用任何一种PC作为服务器,而目它支持无盘工作站(和微机),适合经费不宽裕的学校教学实验室和小企业。但是,这些特色都无法抵消微软在微机操作系统上的优势。事实上,没有多少企业需要将五花八门的计算机连起来,因为大部分企业在建立自己的网络时都会有一个规划。随着硬件价格逐步降低,无盘工作站渐渐变得无人问津。微软只是老老实实地将微机联好,这就解决了百分之八九十的问题,微软吃住了这百分之八九十的市场,就能统治企业级网络操作系统了。
与其他和微软竞争的失败者相比,Novell在和微软的竞争中几乎没犯什么错误。如果说它有什么不足的话,可能是在执行力上比盖茨领导的微软有差距。但是,胜利者只能有一个,只要微软垄断微机操作系统,Novell在操作系统上便注定要输给微软。Novell无疑知道微软的垄断是阻碍它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在2000年美国司法部对微软反垄断的官司中,它是最重要的证人。2000年初审判决将微软一拆为二,Novell原本可以喘口气,但是,2001布什上台后为微软翻了案,Novell从此掉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虽然后来Novell把Linux介绍给了NetWare用户,并把NetWare与Linux结合起来,总算活了下来,但是已经在网络市场上降到二流的地位。2010年在本书第一版中,我们估计“NetWare从企业的视野中消失,只是时间的问题”。果不其然,在金融危机中Novell公司倍受打击,于2011年4月被Attachmate公司收购。之后,Attachmate公司又卖掉了Novell的一些资产(主要是专利),并目大量裁撤了Novell的员工。独立的Novell就此消失了。
3 网景公司
在科技工业史乃至整个工业史上,能超过微软的发展速度并盖过其风头的公司屈指可数。能否超越微软,哪怕在一段时间内标志性地超越微软,也就成了伟大公司的试金石。网景公司是少数曾经盖过微软风头的公司之一。
3.1 昙花一现
网景和微软的网络浏览器(Web Browser)之争已经成为IT史上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们只在这里简要地提一两句,不作详述。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开始兴起。安德森和克拉克为了方便大家浏览互联网,开发了图形界面的网络浏览器。1994年他们成立了网景公司(Netscape),并且成功推出了软件产品“网景浏览器”。很快,这个软件就大受欢迎,不到一年就卖出几百万份。第二年,也就是1995年,成立仅一年的网景公司就挂牌上市了,在华尔街的追捧下,网景的股票当天从28美元涨到75美元,之后一直上涨,速度超过了早期的微软。虽然网景公司已经被炒得很红火,盖茨还是根本没有注意到网络浏览器的重要性,尽管他的顾问们一再提醒他。也许,盖茨最初只是把浏览器当成了一种一般的应用软件,这样的话微软当然不用太在意。相反,华尔街倒是对微软在互联网领域犹豫不前表示不满。同年11月,高盛公司将微软的股票评估从买人下调到持有,微软的股价应声而落。
当同事们再次展示Netscape浏览器时,盖茨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因为,在互联网时代,浏览器是人们通向互联网的入口。要是不能控制浏览器,微软的操作系统控制用户的作用就会减弱。微软必须夺回这个人口,否则将来在互联网上就会受制于人。微软对战略对手的做法一般不外乎三招:合作、收购和倬出杀手锏。对于网景,微软也是先礼后兵,先谈合作与收购。网景这时面对两难的问题,答应微软,从此就受制于人,不答应微软,就可能像莲花公司和WordPerfect一样面临灭顶之灾。最后,网景拒绝和微软合作,决定凭借自己在技术和市场上的优势,和微软正面竞争。
1995年底,微软正式向网景公司宣战。我们在前面介绍微软时已经介绍了这段历史,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开始,由于微软在技术上差距太大,它的浏览器IE 1.0和2.0在市场上对网景的威胁还不是太明显。但是微软依托Windows平台,倬得IE的增长率实际上已经超过 Netscape了。
1997年是个转折年。那年10月,微软发布了性能稳定的IE 4.0。不知是为了重视硅谷的用户和人才,还是为了向网景示威,发布会在远离微软总部的硅谷重镇旧金山举行。当天夜里,微软的员工还跑到网景公司偷营劫寨,将一块大大的IE标志放到了网景公司总部楼前的草坪上。这种恶作剧一般是十几二十岁的工科大学生玩的把戏,比如MIT的学生曾经在哈佛和耶鲁的橄榄球赛场中爆出MIT的标志,康奈尔的学生曾经在万圣节把一个几十斤重的大南瓜插到了学校塔楼的尖顶上。一个大公司的员工玩这种恶作剧的还很少,难怪网景公司的发言人也给逗乐了。
推出IE 4.0之后,微软的浏览器就非常接近当时Netscape浏览器的水平了,在一些性能上甚至各有千秋。这时和Windows捆绑的作用突然显现出来,用户不再下载即倬是免费的Netscape了。网景就被垄断了操作系统的微软用这种非技术、非正常竞争的手段打败。失去市场的网景唯一能做的就是上法庭告微软的垄断行为。
网景对微软的官司旷日持久。虽然法庭在2000年做出了有利于网景公司的裁决,但是在此之前它已经经营不下去了,并目被美国在线收购。
多年后,佩奇在总结网景的教训时,为网景找到了一个可以在微软垄断的压力下生存的办法,易然是马后炮,不过应该是有效的。
3.2 佩奇的解决办法
在Google上市以后,华尔街一度担心Google是否会重蹈网景公司的覆辙,最终被微软靠捆绑手段击败。Google的共同创始人拉里·佩奇在一次会议上谈到了这个问题,他的观点颇有新意而又切实可行。
佩奇的原话我已经记不清了,大意是讲,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网景公司在微软捆绑推广自己的浏览器IE后,注定难逃破产的厄运。当然,微软这种非常规的竞争方法很厉害,但是,网景公司自身也有问题,否则它有可能在微软的压力下生存并发展。网景公司在其浏览器广为用户使用时,没有居安思危,它没有注意去控制互联网的内容,这样一来它失去了保护自己和反击微软的可能性。本来它最有可能成为雅虎。
这里我根据自己的理解,解释一下佩奇的话。
第一,网景没有居安思危。让我们先回到1995年。当微软开始开发浏览器时,网景公司并没有意识到这对自己会产生颠覆性的威胁。这也难怪,因为以往微软击败WordPerfect和莲花公司时,只是利用了自己拥有Windows的优势,而没有赤裸裸地在商业竞争中采用免费的倾销方式。网景当时在技术上明显领先于微软,因为微软早期的IE 1.0和2.0简直就像是大学生做的课程设计,缺陷无数,经常崩溃或者因占用资源太多导致死机,兼容性差,还有很多安全性漏洞。即使是在微软抢走了大部分浏览器市场的头几年里,网景的浏览器仍然比微软的好一些。网景公司当时利润率很高,它认为即使将来打价格战,自己也不见得输(它没想到微软把售价压到零)。
事实证明,网景在技术上的优势是根本靠不住的。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多次介绍了技术领先的产品在商业上失败的例子。网景公司可能没有想到,用户对于网络浏览器根本没有忠诚度可言—一对大多数用户来说,只要给他一个免费的、预装的浏览器,就够用了。在这种情况下用户的流失,要比在一般商业竞争中快得多。1997年,当微软员工将IE的标志放到网景公司门前时,网景公司员工马上回敬了微软,把它换成了自己的标志,并且写上网景72、微软18,表示两个公司当时的市场份额。
但是,网景这个四倍于微软的市场占有率如此不可靠,以至于仅仅一年半以后,就被微软赶超。网景与微软浏览器市场份额的消涨如图14.6所示。
图14.6 网景和微软浏览器的市场份额
第二,网景公司的商业模式还停留在卖软件上。这是微软成功的商业模式,但是其他公司不能直接套用。事实上,当Windows 95出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任何一个世界级的PC软件公司。现在PC世界里仅存活下来的几个世界级的软件公司赛门铁克、Adobe和Intuit不仅都成立于上个世纪80年代(1982年、1982年和1983年),并且在Windows 95推出之前完成了IPO(1989年、1986年和1993年)。在微软垄断了PC操作系统以后,就再也没有像样的软件公司上市并生存下来。原因很简单,如果在PC领域还存在全球性的机遇,那么微软一定不会放过并且将挤垮全部的主要竞争者(Meaningful Players)。网景公司要想逃脱这一厄运,就必须改变商业模式。在1995年,没有哪家公司比网景更有希望成为今天的雅虎。
回顾1995年,全世界互联网的内容易然并不多,但是居然没有一个公司将互联网上杂乱无章的内容组织起来。雅虎仅靠人工就能组织和索引互联网的内容运作,可见当时互联网之小,组织互联网内容之容易。当网景公司搞出Netscape浏览器时,杨致远和费罗还在学习HTTP协议。即倬最初网景看不到索引和组织互联网内容的重要性,但是到1994年底,当雅虎的访问量首次达到一百万次时,网景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了。如果那时候网景公司走门户网站之路,没有人能阻挡它成为后来的雅虎。也许是浏览器卖得太好了,网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雅虎公司成立后,网景公司多多少少看到了雅虎的价值,便为雅虎提供了服务器,却没有出高价收购(或者自己搞一个)。网景公司甚至没有意识到当初其浏览器默认启动页面的价值,轻易就把它给了雅虎,以至于用户一开机就知道雅虎,从而养大了后者。假如时光倒流,不知网景的巴克斯代尔是否会将公司打造成门户网站,但是,如果让今天的佩奇接手当年的网景,他一定会的。
第三,和微软这样实力雄厚、雄心勃勃而执行力奇高的公司竞争,必须有办法顶得住微软的轮番进攻,并目有二次、三次的反击能力。除了上面提到的抢先控制互联网的内容外,另一个主要的方法就是联合PC制造厂商预装Netscape浏览器。这一商业手段的可行性后来已经被Google和雅虎证明了。2006年,微软在新的IE中将MSN的搜索设定为默认搜索引擎,试图再次利用捆绑的优势挤垮雅虎和Google。但是,雅虎和Google防到了微软这招,分别在世界前两大PC厂商惠普和戴尔的电脑出厂前预装了搜索工具条,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微软捆绑搜索的影响。上个世纪90年代,在PC中预装软件的成本比现在还低很多,而网景的浏览器当年是最受欢迎的PC软件之一,因此网景公司应该不难说服PC厂商付费预装自己的浏览器。
第四,网景公司虽然在抓用户,抓的却是买网景公司软件的用户而不是真正倬用互联网的用户。当时正处在互联网发展的初期,一个免费的邮箱对互联网用户有很大吸引力。Hotmail就是靠这一点,便取得了当时互联网全部流量的一半,这是Hotmail的创始人、我的合伙人杰克·史密斯亲口对我讲的。1997年,微软以4亿美元收购Hotmail时,它已经拥有近千万的用户,是当年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如果网景公司能先下手为强,收购Hotmail,它在日后和微软竞争的力量对比上就会发生质的变化。
作为网民上网必不可少的浏览器的发明者,网景公司本来可以成为互联网的领头羊,就像2000年的雅虎和今天的Google。再不济也可以像Adobe和赛门铁克等公司那样成为某个领域的主要厂商(Major Player)。但是,网景公司只辉煌了短短的几年便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网景公司的衰亡固然是微软垄断造成的,但是,它也有摆脱厄运的机会,只是自己没有把握好。
网景公司后来被美国在线收购,在互联网上几乎没有了任何影响力。但是它成为了Google的老师,而它的这个学生没有重蹈覆辙。2008年9月,Google发布Chrome浏览器,重新点燃了浏览器之战,并目不断蚕食微软IE的市场。到2011年3月,Chrome获得了11%的全球市场份额,而从Mozilla发展起来的火狐浏览器(Firefox),当时占了全球三成的市场。同期,微软IE的市场份额从垄断时的九成,跌至不到五成,易然当时微软的IE依然在努力维持市场份额,但是大家都看出来IE的颓势已经显现了。果不其然,仅仅一年之后(2012年),Google的Chrome浏览器市场份额不断增加,微软的IE市场份额不断萎缩,此消彼长,Chrome的市场份额超过了IE。到了2018年,前者独霸了全球的浏览器市场(62%左右)而后者被挤出了前三名(只有2%的市场份额)。这么看来,网景公司也算是薪尽火传了。
4 RealNetworks
当苹果公司的iPod以高科技精品的面孔上市,并风靡全球时,便有行家指出iPod其实并不是什么高科技新品,而是一个翻版的MP3播放器。MP3音乐和播放器大家都很熟悉,它们在iPod上市前好几年就有了,而目最初搞MP3音乐的公司也不是苹果。
MP3是当今在互联网上传播音乐最通用的媒体格式。它的历史十分“悠久”,可以追溯到1979年AT&T贝尔实验室搞的一些语音压缩算法。到了1991年,德国弗劳恩霍夫(Fraunhofer)应用研究所和AT&T贝尔实验室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种对高保真激光唱盘质量的音乐进行有损压缩的音频压缩标准MPEG-1 Audio Layer Ⅲ,简称MP3。采用MP3数据格式的音乐质量比激光唱盘的质量要差一些,不过数据文件要小一个数量级。在互联网兴起以前,这种音频压缩方法并未得到广泛应用。1995年,弗劳恩霍夫基于MP3格式推出了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运行的世界上第一个MP3播放器软件WinPlay3。互联网兴起后,大家发现音乐经过压缩,在互联网上传播成为可能。在MP3以后,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音频文件压缩方法。
1995年,微软的一位高管罗伯·格拉泽(Rob Glaser)离开微软,创办了RealNetworks公司。它一方面开发适用于互联网的通用音频和视频播放器,另一方面为媒体公司如NBC提供将节目放到互联网上的服务。该公司的播放器是跨平台的,支持所有现有的音频和视频压缩格式,支持边下载边播放(而不是下载完了再播放),并根据网络传输速度的快慢调整音频和视频质量(网络传输速度越快,质量越高)。
RealNetworks早期非常成功,创办的当年就推出了播放器RealPlayer 1.0,并目在互联网上转播了NBA的篮球比赛。在接下来的两年里,RealNetworks每半年就推出一些新产品和服务。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微软在播放器市场上地位的加强,RealNetworks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制约。和微软的IE一样,其媒体播放器Windows Media Player也是随Windows操作系统免费提供的。很快,微软的Media Player就超过了RealPlayer,一举夺得市场占有率第一,这里面盗版的Windows也为微软抢夺播放器的市场份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了免费的播放器,很少有人会花40美元下载一个功能差不多的RealPlayer了(RealNetworks通常让用户免费下载它的旧版播放器,但又功能不全,它最新的播放器在美国始终要价39.99美元,直到后来它将商业模式改成从付费内容的流媒体收费为止)。当然,由于专利的限制,有些格式的媒体不能用微软的Media Player播放,必须用RealPlayer付费版播放,但是,如果哪家媒体公司选择了这种格式,观众和听众数必然少而又少,久而久之,这种不能通用的媒体格式便自然而然地趋于淘汰。到2000年,网络上绝大多数媒体都采用微软播放器可以播放的格式。这样一来,微软利用免费捆绑的Media Player,又控制了广大用户计算机上的播放器,进而渐渐控制了互联网上的媒体文件格式。
微软从1998年起在播放器上挑战RealNetworks,到2000年前后便夺取相当于RealPlayer一半的市场份额(ACNielsen和comScore等第三方市场研究公司发布的播放器市场的占有率数据大相径庭,这里只能给出一个大致估计),到了2002年,两家公司在这个市场上已平分秋色了。两年后,RealPlayer的占有率不到微软Media Player的一半,以后逐年减少。到2009年RealPlayer的占有率已不到播放器市场的20%,如图14.7所示。再往后,由于它的用户基数越来越少,视频内容制作商甚至懒得提供RealPlayer格式的新内容了。这样,RealNetworks就完成了它的历史倬命。
图14.7 媒体播放器市场份额演变
RealNetworks源于微软又被微软打败。易然它的境遇和网景公司有些相似,但是,两家公司失败的原因却不尽相同。网景公司是被动地死守浏览器市场,但是在微软捆绑的打击下节节败退,最后无险可守,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RealNetworks也许因为是微软自己人办的公司,谙熟微软的竞争之道,所以一开始就不断在找退路,它在做播放器的同时,提供了多项基于互联网的广播和电视服务。RealNetworks通过向互联网用户收订阅费(Subscription Fee)挣钱,同时在广播和电视中插播一些广告。除此之外,它还有音乐付费收听和视频付费收看等。比如在网上听歌每月13美元,网上玩游戏每月10美元。由于RealNetworks比较早进入服务市场,同时服务市场又一直是微软的弱项,它在失去了播放器软件市场后,终于守住了网络音频和视频服务的市场。服务收人在RealNetworks营业额中的份额,最初是空白,但是逐年增加,2007年达到了83%,如图14.8所示。
图14.8 RealNetworks服务收入的增长趋势
靠着付费服务的收人,RealNetworks挺过了从2000年到2002年互联网最艰难的时期,得以生存下来。但是RealNetworks的营业额始终没有回到2000年的水平,华尔街也很不看好它。它的股价从2000年初的90多美元降到2001年3美元的最低点,之后一度恢复到30美元以上,但随后几年一直维持在10美元以下。此后,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RealNetworks基于PC的生存环境不在了,便从此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过,在互联网历史上,RealNetworks的贡献不可磨灭。它倬得音乐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当然这里面Napster的贡献也很大)。在网络泡沫破碎前(2000年),音乐占整个互联网流量的第二位。
其实,RealNetworks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抵御微软的竞争,那就是走后来苹果iPod的道路,推出自己的便携式媒体播放器,这样它就有希望赶上移动互联网的大潮,重现辉煌。也许是因为RealNetworks源于微软,故而不自觉地采用了卖软件的商业模式,而没有想到做一个类似iPod的消费电子产品。也许是因为在Napster输了和唱片公司的官司后,RealNetworks看不到网上音乐市场的前景,便把精力集中在将新闻等电视节目搬到网络上,这其实是一次没有意义的转型。美国广大观众至今仍然习惯于在大屏幕电视上看新闻,而不是到计算机的小屏幕上看豆腐块大的视频。至于听歌,大家后来是的习惯是在iPod、iPad和手机上听,而这些都与RealNetworks无关。
总的来讲,RealNetworks属于上一代的互联网和多媒体公司。RealNetworks能够在和微软竞争中幸存下来,非常不容易,这是它谙习微软竞争之道的结果。但是,它一直没有找到超越那个时代的商业模式,这同样也是它深受微软影响的结果。其实,RealNetworks曾有希望成为YouTube或者奈飞那样的公司,但是在RealNetworks诞生的年代,网速过慢,想打造YouTube那样的在线服务完全是天方夜谭,因此YouTube和奈飞的商业模式从来就没有存在于它的基因中。当后来大的环境变化后,RealNetworks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而作为一个纯软件公司,它也不具备苹果做硬件设备的基因,因此本来它最有资格成为早期便携式媒体播放器的霸主,也和那次机会失之交臂了。这在表面上看是二流公司和苹果、Google(YouTube的母公司)那样的一流公司之间的差距,但更多地则是基因倬然。
结束语
从太阳公司到RealNetworks,都在短短的几年到十几年时间里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再到顶点的过程,然后便迅速地衰落。易然它们最终是败在了微软的手下,但是它们的衰退很大程度上都是自身原因造成的(Novell自身的原因少一些)。如果它们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就能在与微软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甚至竞争成败的本身都变得不很重要,因为它们毕竟曾经有机会开拓微软所不涉及的领域。如果把这些公司放在更长的历史阶段来看,它们则都有存在的意义,因为它们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代表了科技产业发展的方向。太阳公司不但代表了网络时代计算机系统方面的成就,而且提供了互联网时代大家可以一起工作的一个软件平台JAVA。Novell公司则是局域网时代的技术代表,它的网络操作系统在一定意义上是今天云计算操作系统的前身。网景公司提供了用户可以方便上网的工具,而RealNetworks则是后来在线媒体播放器的前身。它们在IT产业的特定时间点都有它们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然而,IT产业是快速变化的、竞争激烈的,因此它们都成了和微软竞争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它们也是自身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失败者。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失败可以成为成功之母,从它们身上吸取了教训的新一代企业,在避免了它们的失误之后,成为它们所开创产业的受益者。太阳公司的操作系统和今天Google、亚马逊甚至微软云计算的内核非常相似,甚至它的RISC处理器设计,也为今天数据中心使用的低功耗芯片提供了经验。Novell的网络操作系统在功能上和后来亚马逊的云计算是重叠的。RealNetworks失败了,但是YouTube和奈飞却成功了。网景公司消失了,Google的Chrome却战胜了IE。后者对前者的超越,是IT产业不断进步的原因。在赞扬今天那些成功的企业给我们带来高技术的产品和服务时,我们也应该感谢这些只有短暂光辉的公司。
第15章 幕后的英雄 风险投资
任何一家公司的创办都离不开资金。传统上创业资金的合法来源只有两种渠道:第一种是靠积累(比如继承遗产或是自己多年的积蓄),第二种是靠借贷(比如从家人、亲戚和朋友那里凑钱,或者从银行抵押贷款)。如果要求创业者将全部积蓄倾囊而出进行创业,很多人可能会知难而退,更何况最喜欢创业的年轻人恰恰是积蓄最少的群体。从银行贷款必须要有财产可抵押,对于有房子的人来说最值钱的就是房子,但是房子一旦抵押出去很可能赎不回来,自己便无家可归了,何况也不是人人都有房子可抵押。因此,年轻人要通过这两种传统途径获得创业资金很不容易。这样,资金就成了创业的瓶颈。在很多国家,包括几乎整个欧洲,很少能看到新的公司兴起,原因就是没有人愿意提供创业的资金。
美国是一个富于冒险精神的年轻的国度。二战后,尤其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愿意以高风险换取高回报的投资人发明了一种非常规的投资方式一一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简称VC),在中国又简称风投。风险投资和以往需要有抵押的贷款有着本质的不同。风险投资无需抵押,也不需要偿还。如果投资成功,风投资本家将获得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回报,如果投资失败,钱就打水漂了。对创业者来说,利用风险投资创业,即倬失败也不会背上债务。这样就使得年轻人创业成为可能。几十年来,这种投资方式总的来说非常成功,硅谷在创造科技公司神话的同时,也创造出另一个神话—一投资的神话。
1 风投的起源
……
对私有企业的投资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收购长期盈利看好但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比如投资大师巴菲特就经常这么做,他很成功的案例是在美国大保险公司Geico(原名政府雇员保险公司,Government Employee Insurance Company)快要破产时,以超低价全面收购了该公司,并将其扭亏为盈,从而获得了几十倍的收益。一些基金专门做这样的投资,它们通常被称为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s)。另一种是投资一个初创小公司,将它做大上市或被其他公司收购。后者就是风险投资的对象。
和抵押贷款不同,风险投资是无抵押的,一旦投资失败就血本无归。因此,风投资本家必须有办法确认接受投资的人是老老实实用这笔钱创业的实业家,而不是卷了钱就跑的骗子(事实上,风险投资钱被骗的事件还时有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经过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总统的努力,美国建立起了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Social Security System)和信用制度(Credit System),倬得信用(Credit)成为美国社会的基础。每个人(和每家公司)的信用记录都可以通过其社会保险号查到。美国社会对一个人最初的假定都是清白和诚实的(Innocent and Honest),但是只要发现某个人有一次不诚实的行为,这个人的信用就完蛋了一—再不会有任何银行借给他钱,而他的话也永远不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诚信上犯了错误,改了也不是好人。全美国有了这样的信用基础,银行就敢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把钱借出去,投资人也敢把钱交给一无所有的创业者去创业。不仅如此,只要创业者是真正的人才,严格按合同去执行,尽了最大努力,即倬失败了,风投公司以后还会愿意给他投资。美国人不怕失败,也宽容失败者。大家普遍相信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一点在其他国家很难做到(当然,如果创业者是以创业为名骗取投资,他今后的路便全被堵死了)。美国工业化时间长,商业发达,与商业有关的法律健全,也容易保护风险投资。
相比其他发达国家,美国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很多美国人是第一代移民,爱冒险,而且想象力丰富,乐于通过创业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美国的大学总体水平世界领先,并目在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平衡得比较好,容易做出能够产业化的发明创造。这两条加在一起,倬得风险投资人比较容易发掘到好的投资项目和人才。上述这一切原因凑到一起,就形成了风险投资出现和发展的环境。
高回报的投资一定伴随着高风险,但反过来高风险常常并不能带来高回报。任何一种长期赚大钱的金融投资必须有它内在的动力做保证。股市长期来讲总是呈上涨趋势的,因为全世界经济在发展。风险投资也是一样,它内在的推动力就是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由于新的行业会不断取代老的行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专门投资新兴行业和技术的风险投资从长期来讲回报必定高于股市。风险投资看上去风险大,但并不是赌博,它和私募基金都是迄今为止收益最高的投资方式平均年(回报率大致在15%——20%左右)。正是鉴于其高回报,不断有个人和机构(Institute)愿意将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基金,比如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将退休基金的很大一部分放到风投公司凯鹏华盈(KPCB)近30年来,风投基金越滚越大,从早期的一年几万美元,到过去20年每年在400亿美元左右风险投资甚至不分国界,如果世界其他国家有更好的投资项目,美国风险投资基金也会跨境投资,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投在了中国和印度,少部分投在了以色列(欧洲的风投至今仍然很少)。
从财务和税务上讲,风险投资和传统的私募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类似,但是它们的投资对象和方式完全不同。私募的投资对象大多是拥有大量不动产和很强现金流(Cash Flow)的传统上市企业,这些企业所在的市场被看好,但是这些企业因为管理问题,不能盈利。私募基金收购这些企业,首先让它下市,然后采用换管理层、大量裁员、出售不动产等方式,几年内将它扭亏为盈。这时,或者让它再上市,比如高盛收购汉堡王(Burger King)后再次上市;或者将它出售,比如Hellman & Friedman基金收购双击广告公司(DoubleClick),重组后卖给Google。运作私募基金要求能够准确估价一个问题重重的公司,具有高超的谈判技巧和资金运作本领,但是最关键的是要能摆平劳工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蓝领的工人和工会(因为私募基金一旦收购一家公司,第一件事就是卖掉不良资产和大规模裁员)。从这个角度上讲,私募基金是在和魔鬼打交道,但它们是更厉害的魔鬼。
风险投资则相反,他们是在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打交道,同时他们又是更聪明的人。风险投资的关键是准确评估一项技术,并预见未来科技的发展趋势。所以有人讲,风险投资是世界上最好的行业。
要了解风投首先要了解它的结构和运作方式,然后了解风投的决策。
2 风投的结构
风险投资基金(Venture Capital Funds)主要有两个来源:机构(Institute)和非常富有的个人。比如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基金会就属于前者。当然,为了让投资者放心,风险投资公司自己也会出资一起投资。
风险投资基金一般是由风险投资公司出面,邀集包括自己在内的不超过499位投资者(和投资法人),组成一个有限责任公司(Limited LiabilityCompany,LLC)。为了避税,在美国融资的基金一般注册在特拉华州,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融资的基金注册在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或巴哈马(Bahamas)等无企业税的国家和地区(如果读者创业时遇到一个注册在加州或纽约的美国基金,那一定是遇到骗子了)。为什么不能超过499人呢?因为根据美国法律规定,一旦一家公司的股东超过500人并具备一定规模,就必须像上市公司那样公布财务和经营情况。而风险投资公司不希望外界了解自己投资的去处和资金的运作,以及在所投资公司所占的股份等细节,一般选择不公开财务和经营情况,因此股东不能超过500人。每一轮基金融资开始时,风投公司要到特拉华等地注册相应的有限责任公司,在注册文件中约定最高的融资金额、投资的去处和目的。风险投资公司会定一个最低投资额,作为每个投资人参与这一期投资的条件。比如红杉资本一期融资常常超过10亿美元,它会要求每个投资人至少投人200万美元。显然,这只有机构和非常富有的个人才拿得出。
风险投资公司每融资一次便成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它的寿命从资金到位(Close Fund)开始到所有投资项目要么收回投资,要么关门结束,一般历时10年左右,前几年是投入,后几年是收回投资。一家风险投资公司通常定期融资,成立一期期的风险基金,基金为全体投资人共同拥有。风险投资公司扮演总合伙人(General Partner)的角色,国内有些地方将它翻译成普通合伙人,这是字面翻译,含义不准确,这里面的General和总经理General Manager里面的General是一个含义。其他投资者称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也就是人们有时讲的出资人。总合伙人除了拿出一定资金外,同时管理这一轮风险基金。有限合伙人参与分享投资回报,但是不参与基金的决策和管理。这种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可以保证总合伙人能够独立进行投资,不受外界干扰。为了监督总合伙人的商业操作和财务,风投基金要聘请独立的财务审计顾问和总律师(Attorney in General),这两者不参与决策,但是他们有责任监控风险。风险投资比炒股风险更高,一旦出错,基本上是血本无归。为了减少和避免错误的决策,同时替有限合伙人监督总合伙人的投资和资本运作,一家风投基金需要有一个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或顾问委员会(Board of Advisors)。这些董事和顾问要么是商业界和科技界的精英,要么是其他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人。他们会参与每次投资的决策,但是决定由总合伙人来做。
风险投资到了中国之后,出现了少许变化。首先很少有上百个有限合伙人参与基金的情况,即使基金的规模很大,常常也是由几个大的有限合伙人出资,甚至会出现一两个投资人提供绝大部分资金的情况。遇到最后一种情况,这样的投资人甚至会要求同时担任总合伙人,参与投资分成,这基本上是中国特色。另外,中国很多小的基金规模极小,投资决策就是一两个总合伙人拍板,并没有严格遵守程序,行为极不规范。
风险投资基金的总合伙人的法人代表和基金经理们一般都很懂技术,很多人都是技术精英出身,他们自己还成功创办过科技公司。比如被称为世界风投之王的约翰·杜尔(John Doerr)原来是英特尔公司的工程师。中国由海归创办的最大的三家风投公司北极光(Northern Light)、华山资本(West Summit)和赛伯乐(Cybernaut)的创始人以前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比如创办北极光创投的邓锋和柯严博士,原来是全球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公司NetScreen的创始人,同时是网络安全领域的专家。华山资本的共同创始人陈大同是著名的OmniVision和展讯两家上市公司的创始人,另一名共同创始人杨镭也曾担任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首家中国无线娱乐公司掌上灵通的CEO。赛伯乐的创始人朱敏博士是全球最大的电话电视会议技术和服务公司WebEx 的创始人。为了跟进最新技术,风险投资公司会招很多技术精英,同时还会请外面的技术顾问,比如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一起来帮助评估每一项投资。最近几年(2015年之后),由于出现了投资泡沫,很多新的小基金总合伙人完全没有行业经验,一些人只工作过一两年,甚至有的刚离开学校,就负责投资了,这样的基金风险极高,而且鲜有成功的,以至于很多人把风险投资和骗子划上了等号。在接下来介绍风险投资时,就不把这种基金算成是正规的基金了。
风险投资基金一旦进人被投的公司后,就变成了该公司的股东。如果该公司关门了,相对于公司创始人和一般员工,风投基金可以优先变卖公司资产收回部分投资。但是,这时能拿回的钱通常比零多不了多少。如果投资的公司上市或被收购,那么合伙人或者直接以现金的方式收回投资,或者获得可流通的股票,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前者一般针对较小的基金和较少的投资,总合伙人会在被投资的公司上市或被收购后的某一个时间点(一般是在锁定期(Lock-up Period)以后)卖掉该基金持有的全部股票,将收人分给各个合伙人。这样的基金管理成本较低。但是,如果基金所占股份较大,比如风险投资在很多半导体公司中常常占到股份的一半以上,这种做法就行不通了。因为上市后一下子卖掉其拥有的全部股票,该公司的股价会一落千丈。这时,风险投资的总合伙人必须将股票直接分给每个合伙人,由每个合伙人自己定夺如何卖掉股票,从而避免股票被同时抛售的可能性。易然这么做基金管理的成本(主要是财务上的成本)增加了不少,但是大的风投公司必须这么做,比如凯鹏华盈和红杉资本各自拥有几十亿美元Google股票,如果这些股票在Google上市180天后一下子涌到股市上,就会造成Google股价大跌,于是两家风投将股票分给了有限合伙人,由他们自行处理。事实上大部分合伙人都没有抛售,结果Google的股价在180天后不跌反涨。
为了降低风险,一轮风投基金必须投十几到几十家公司。当然,为了投十家公司,基金经理可能需要考察几百家公司,这笔运作费用不是小数目,必须由有限合伙人出资,一般占整个基金的2%。风投公司总合伙人还要从有限合伙人赚到的钱中提取一部分利润,一般是基本利润(比如8%)以上部分的20%。比如某个风投基金平均每年赚了20%的利润,总合伙人将提取(20%–8%)×20%=2.4%,外加2%的管理费,共4.4%,而有限合伙人得到的回报为15.6%,只相当于总回报的3/4。如果风险投资的回报很高,比如超过了三倍,总合伙人提取的利润比例还会增加。由此可见,风投公司的收费其实非常高昂。
管理风投基金的风投公司本身也是一个美国的有限责任公司(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LLC),最高管理者就是风投公司的合伙人(Partners),不会有什么CEO、总裁之类的头衔(有这些头衔的风投公司一定是冒牌货)和职务。合伙人有两个特征,首先合伙人之间彼此是平等的,其次他们在公司内部地位很高,而目常常还在科技界呼风唤雨,比如KPCB的合伙人约翰·杜尔就是Google、太阳、亚马逊等多家上市公司和更多未上市公司的董事。
在风投刚刚进入中国时,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在一次风险投资研讨会上,来了很多公司的CEO、总裁等“贵宾”,礼仪小姐一看这些人的职务,便把他们请到前排入座。后来来了一位客人,礼仪小姐一看是什么合伙人,便将他安排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就座。这位合伙人没说什么就在后排坐下了。结果那些CEO和总裁看他坐到了最后,谁都不敢往前面坐了,因为这些CEO和总裁所在的公司都是他投资的,而他们的职位也是他任命的。由此可见风投合伙人在业界的影响力。
大的风险投资公司每一轮融资的资金都很多,比如硅谷的红杉资本和NEA一轮基金动辄十几亿美元,如果每家公司只投资一两百万美元,一来没有这么多公司可投,二来即倬有,总合伙人要在几年里审查几千几万家公司,显然也不现实,因此它们每一笔投资都不能太小;而另一方面,新成立的公司本身都很小,尤其是初期,它们只需要融资几十万甚至几万美元就可以了,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就不会参与。对于这些公司的投资,就由一类特殊的风险投资商一一天使投资人来完成。
天使投资(Angel Investment)本质上是早期风险投资。天使投资人,简称天使,常常是这样一些有钱人:他们很多人以前创办过成功的公司,对技术很敏锐,又不愿意再辛辛苦苦创业了,希望出钱让别人干。在硅谷这样的人很多,他们的想法就是“不愿当总(经理),只肯当董(事)”。
一些天使投资人会选择独立寻找项目进行投资,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几个人凑到一起组成一个有限责任公司(LLC)或有限伙伴关系(Limited Partnership,LP),通常称作天使投资社(Angel Firm)来共同投资。天使投资社的经营管理方法千差万别,有的是大家把钱凑在一起,共同投资;有的是每个人各自选项目进行投资,同时介绍给社里,社里会加倍投人(Match)该天使投资人所投的金额。约翰·杜尔和迈克尔·莫里茨投资Google时就是采用这种策略,他们两人都自掏腰包拿出一些钱投给Google,同时他们所在的凯鹏华盈和红杉资本拿出同样(可能更多)的钱也投给了Google。当然,有些天使投资社管理更灵活,某个天使投资人投资一家公司后,其他合伙人可以选择跟进(Follow),也可以不跟进(Pass),没有什么义务,大家坐到一起只是为了讨论一下问题而已,共同倬用一个律师和会计。
了解了风险投资的管理结构,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公司是如何投资的。
3 风投的过程
风险投资的过程,其实就是一家科技公司创办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中美两国是有差异的,由于风险投资起源于美国,我们这里以美国的投资过程为准。在美国,一家新兴科技公司(Startups)的创办过程通常是这样的:来自思科公司的工程师山姆和IBM公司的工程师强尼发明了一种无线通信的技术,当然这种技术和他们所在公司的核心业务无关,两人觉得这种技术很有商业前景,就写了个专利草案,又花5000美元找了个专利律师,向美国专利局递交了专利申请(关键之一,知识产权很重要)。两个人将业余时间全泡在山姆家的车库里,用模拟软件MATLAB进行模拟,证明这种技术可以将无线通信速度提高50倍(关键之二,有无数量级的提高是衡量一项新技术是革命性的还是革新性的关键)。两个人设想了好几种应用,比如代替现有的计算机Wi-Fi,或者用到手机上,于是在原有的专利上又添加了两个补充性专利。接着,强尼和山姆拿着投影胶片、实验结果和专利申请材料到处找投资者,在碰壁七八次以后,找到了山姆原来的老板,思科早期雇员亚平。亚平从思科发了财后不再当技术主管了,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有钱人一起在做天使投资人。亚平和不下百十来个创业者谈过投资,对新技术眼光颇为敏锐,发现山姆和强尼的技术很有独到之处,但是因为山姆和强尼说不清楚这种技术的具体商业前景在哪里,建议他们找一个精通商业的人制定一个商业计划(关键之三,商业计划很重要)。
强尼找到做市场和销售的朋友迪克,并向迪克大致介绍了自己的发明,希望迪克加盟共同开发市场。迪克觉得和这两个人谈得来,愿意共同创业。这时出现了第一次股权分配问题。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工作都是山姆和强尼做的,两个人各占未来公司50%的股权和投票权。迪克加盟后,三个人商定,如果迪克制定出一份商业计划书,他将获得20%的股权,山姆和强尼将减持到各占40%。经过调查,迪克发现山姆和强尼的发明在高清晰度家庭娱乐中心的前景十分可观,于是制定了可行的商业计划书,并得到了20%的股权。三个人到目前为止对今后公司的所有权见表15.1。
表15.1三位合伙人对公司所有权比例
三个人再次找到亚平,亚平请他的朋友、斯坦福大学电机工程系的查理曼教授作了评估,证实了山姆等人的技术非常先进且有相当的复杂度,而目有专利保护,不易抄袭模仿。亚平觉得可以投资了,他和他的天使投资团认为山姆、强尼和迪克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值(未融资前)150万美元,而三个创业者觉得他们的工作值250万美元,最后商定为200万美元。(对公司的估价方法有按融资前估价,即Pre-Money,以及融资后估价,即Post-Money两种。从本质上讲,这两种方法是一样的,我们这里的估计都以Pre-Money来计算。)亚平及其投资团投人50万美元,占20%的股份。同时,亚平提出下列要求:
- 亚平要成为董事会成员;
- 山姆、强尼和迪克三人必须从原公司辞职,全职为新公司工作,并且在没有新的投资进来以前,三个人的工资不得高于每月4 000美元;
- 山姆等三人的股票必须按月在今后的4年里逐步(Vested)获得,而不是在公司成立时立即获得。这样有人中途离开就只能得到一部分股票;
- 如有任何新的融资行为,必须通知亚平的天使投资团。
现在山姆等人就必须正式成立公司了。为便于将来融资和开展业务,他们在特拉华州注册了赛通科技有限公司。山姆任董事会主席,迪克和亚平任董事。山姆任总裁,强尼任主管技术的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迪克任主管市场和营销的副总裁。三个人均为共同创始人。公司注册股票1500万股,内部核算价格每股0.2美元。
在亚平投资后(的那一瞬间),该公司的内部估值已经从200万美元增加到250万美元,以每股0.2美元计算,所有股东的股票为1250万股(250万美元÷0.2美元/股=1 250万股)。那么为什么会多出来250万股,它们并没有相应的资金或技术做抵押,这些股票的存在实际上稀释(Dilute)了所有股东的股权。为什么公司要印这些空头钞票呢?因为公司必须留出它们以应对下面的用途:
- 由于山姆等人的工资很低,他们将按各自贡献,拿到一部分股票作为补偿;
- 公司正式成立后需要雇人,需要给员工发股票期权;
- 公司还未招揽一些重要的成员,包括CEO,他们将获得相当数量的股票。
现在,该公司各位股东股权如表15.2所示。
表15.2第一轮融资后公司股东股权比例及价值(股权比例四舍五入到整数百分比)
接下来,山姆等人辞去原来的工作,全职创业。公司很成功,半年后做出了产品的原型(Prototype)。但是,50万美元投资已经花完了,公司也发展到20多人。250万股票也用去了150万股。这时,他们必须再融资。由于该公司前景可观,终于得到了一家风投如红杉资本的青睐。红杉资本为该公司作价1500万美元,这时,该公司的股票每股值1美元了,比亚平投资时涨了四倍。红杉同意投资500万美元,占25%股份,这样总股数增加到2000万股。同时,红杉资本将委派一人到该公司董事会任职。山姆等人还答应,由红杉资本帮助寻找一位职业经理人任公司的正式CEO。双方还商定,融资后再稀释5%,即100万股,为以后的员工发期权。现在该公司股权如表15.3所示。
表15.3第二轮融资后公司的股权比例及价值
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红杉资本现在已经成了最大的股东。
两年后,该公司的样品研制成功,并获得东芝公司的订单,同时请到了前博通公司的COO比尔出任CEO。比尔进人了董事会,并以每股3美元的价钱获得100万股的期权。当然新来的员工也用去一些未分配的股票。这时该公司的股价其实比红杉资本投资时,已经涨了两倍。比尔到任后,公司进一步发展,但仍没有盈利。于是,董事会决定再一次融资,由红杉资本领头协同另两家风投投资1500万美元。公司在投资前作价一亿五百万美元,即每股5美元。现在,该公司股权变为表15.4所示。
表15.4第三轮融资后公司的股权比
这时,投资者的股份已占到44%,和创始人相当,即拥有了一半左右的控制权。又过了两年,该公司开始盈利,并在某家投资银行比如高盛的帮助下增发600万股,在纳斯达克上市,上市时原始股定价每股25美元。这样,一个科技公司在VC的帮助下便创办成功了。上市后,该公司总市值大约七亿五千万美元。该公司股权分配如表15.5所示。
表15.5 第四轮融资后公司的股权比例及价值
这时,创始人山姆等人成了充满传奇色彩的亿万富翁,其员工共持有价值近5000万美元的股票,不少也成了百万富翁。但是,山姆等全体公司员工只持有44%的股份,公司所有权的大部分从创始人和员工手里转移到投资者手中。一般来讲,创始人在公司上市时还能握有10%的股份已经很不错了。
作为最早的投资者,亚平的天使投资团收益最高,高达124倍。红杉资本的第一轮获利24倍,第二轮和其他两家风投均获利4倍。显然,越早投资一个有希望的公司获利越大,当然,失败的可能性也越大。一般大的风投基金都会按一定比例投入到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这样既保证基本的回报,也保证有得到几十倍回报的机会。
我不厌其烦地计算每一个阶段创始人和投资人的股权和价值,是想让那些想求助于风险投资创业的人有一些实际的数量概念。我遇到了许多创业者,他们在接触投资人时几乎毫无融资的经验,有些漫天要价,有些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我们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风险投资必须是渐进的,在每一个阶段需要多少钱,投人多少钱,这样对投资者和创业者都有好处。对投资者来讲,不可能一开始就把今后5年的开销全包了,这样风险太大。对创业者来讲,公司初期股价都不会太高,过早大量融资会将自己的股权稀释得过低,不但在经济上不划算,还可能失去对公司的控制,甚至创业创到一半就被投资者赶走。在上面的例子中,天使投资人和风投一共投人2050万美元,在上市前占有43%的股份,三个创始人和其他员工占57%。如果在最初公司估价只有200万美元时就融资2000多万美元,到上市前,投资方将占股份的80%以上,而创始人和员工占不到20%。
以上是一个简化得不能再简化的投资过程,任何一个成功的投资都要复杂得多。比如,通常天使投资人可能是几家而不是一家,很多人都会要求进人董事会,以致等到风险投资公司真正投资时,董事会已经变得臃肿不堪。在这种情况下,风投公司通常会以当时的合理股价(Fair Market Value)从天使投资人手中买回股权,并把他们统统从董事会中请出去。否则每次开董事会坐着一屋子大大小小的股东,大家七嘴八舌,还怎么讨论问题。大部分天使投资人也愿意兑现他们的投资收益,以降低投资风险。
上面这个例子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情况,该公司的发展一帆风顺,每一轮估价都比前一轮高,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不少公司在某一轮风投资金用完之际,业绩上并没有太大的起色,下一轮融资时估价还会下降。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在这样一家半导体公司工作,他们花掉近亿美元的投资,公司仍旧未能盈利,这样必须继续融资,新的风投公司给的估价只有前一次估价的1/30,但是创始人和以前的投资人不得不接受这个估价,不然公司关门,那样他们的投资一分钱也拿不回来。
4 决策和估价
我们在上一节中举了一个风投投资的例子,其中我们忽略了两个关键问题:风险投资公司如何决定是否投资一家公司(或者一个产业),以及如何决定一个小公司的价值。这两个问题要回答清楚需要专门写一本书,因为每一次投资的情况都不相同,前一次投资的案例通常不能用到下一次。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些投资和估价的原则。
从前面的例子可以看出,风投常常是分阶段的,可以有天使投资阶段、第一轮和后一轮(或者后几轮)。天使投资阶段的不确定性最大,甚至无章可循,很多成功的天使投资回想起来都不知道是如何成功的。一开始投资Google的一些天使投资人,包括政治家亨利·基辛格、演员和加州州长施瓦辛格,以及篮球明星奥尼尔,都搞不清楚Google是干什么的。NetScreen的共同创始人柯严和我讲过他们是如何融到第一笔资金的。谢青、邓锋和他三人在创办NetScreen公司时,开始融资并不顺利,后来他们阴错阳差地从一个台湾的天使投资人那里拿到50万美元。这个投资人根本就不是IT领域的,也搞不懂他们要干什么,最后请了一位相面先生给他们三个人看了看相,看这三个人身材高大,面相也不错,于是那位投资人就投资了。当NetScreen公司以几十亿美元的高价被收购时,这位天使投资人也许应该感谢那位相面先生,为她带来了上百倍的投资收益。关于天使投资的特点,下一节再详细介绍。
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很多大的风险投资公司都选择跳过这一轮。一些更加保守的风投基金只参与最后一轮的投资,比如我在2008年和几位投资人一同成立中国世纪基金时,就恪守只投最后一轮的原则,明确规定下面几种情况下不投资:
- 不盈利的不投;
- 增长不稳定的不投;
- 公司达不到一定规模的不投。
后来创办丰元资本时,我们规定下面三种项目不投:
- 投资周期过长的,比如生物制药不投;
- 美国的旧式工业(Legacy Industry),比如半导体不投;
- 需要靠政府补贴的,比如新能源不投。
有些风投基金在投资时规定更严格,比如只投12—24个月内有上市计划的公司。当然,到了快上市的时候,常常是融资的公司挑选风投了,而不是谁想投资就能投进去的。这时候,能投进去的基金要么是在IT界路子很广的公司,要么是很有名的公司,以至于新兴公司上市时要借助它们的名头。通常,当股民们看到某家将要上市的公司是凯鹏华盈或红杉资本投资的,他们会积极认购该公司上市发行(IPO)的股票。
比较复杂的是中间的情况。下面来看两个我遇到的真实例子,读者就会对风投的决策过程和评估股价方法有所了解。
某名牌大学的一位学生开发了一种手机软件,非常有用,他在网上让人免费下载试用,然后在试用期满后向愿意继续倬用的用户收一些钱,几年下来他也挣了十来万美元。他想成立一家公司把这个软件做大做好。他找到一家风投,正巧这个风投基金的总合伙人是我的朋友,就拉我一起和这位创业者面谈。我们仔细听了他的介绍并目看了他的软件。投资人认可他是个有能力的年轻人,软件也不错,但是不投资。投资人给他算了一笔账。这种手机软件要想推广,必须在手机出厂时预装,一般来讲,虽然这种软件的零售价可以高达10美元以上,但是手机厂商出的预装费不会超过一毛钱,假定为0.08美元。通常一个领域在稳定的竞争期会有三个竞争者,不妨假设这个创业者能跻身于三强并排到老二。在软件业中,一般前三名的市场份额是60%、20%和10%(剩下10%给其他的竞争者),那么在非常理想的情况下,这位创业者可以拿到全世界20%的手机市场的预装权。我们不妨假设全世界手机一年销售10亿部,他可以拿到两亿部的预装权,即一年2000万美元的营业额。读者可能会觉得2000万美元不是小数,但在风投眼里却不算什么,在美国一个工程师一年的开销就要20万美元。世界上有四五个国家近十个主要手机厂商,要想拿下这20%的市场需要一家一家谈。手机的软件不像个人电脑的软件,有了漏洞(Bug)在网上发布一个补丁自动就补上了,手机软件出了问题有时要将手机回收,因此手机厂商测试时间很长,拿下一个手机合同一般要18个月,可见这款软件的销售成本非常高。我们不妨假设这个小公司的纯利润率有15%(已经不低了),那么它一年的利润是240万美元,易然读者觉得一年挣几百万美元已经不错了,但是因为这个生意不可能成长很快(取决于手机市场的成长),在股市上市盈率(P/E值)平均也就是20倍,那么这家公司的市值最多不超过5000万美元。一个价值不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是在美国是无法上市的,因此这家公司还未创办,就注定无法上市了。这位同学失败的原因不在技术上,不在他个人的能力,而是题目没有选好。风投喜欢的是所谓的10亿美元的生意(Billion Dollar Business)。最后,我做风投的朋友建议这位同学找找天使投资人,因为这样一件事做好了还是有利可图的,也许会有天使投资人喜欢投资。
风投是高风险的,自然要追求高回报。每当创业者向我介绍他们的发明时,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保证把一块钱变成五十块?”虽然风险投资最终的回报远没有几十倍,但是,投资者每一次投资都会把回报率定在几十倍以上(上面那个手机软件显然达不到)。因此,我这第一句话通常就难倒了一多半创业者。大部分人听到这句话的反应是:“要这么高的回报?是不是太贪了?两年有个三五倍就不错了吧?”一般传统的投资几年有个三五倍的回报确实已经很不错了,但是风投失败的可能性太大,它必须把回报率定得非常高才能收回整体投资。据我一位做风投的朋友讲,红杉资本当年投资Google的那轮风投基金高达十几亿美元,只有Google一家投资成功了,如果Google的回报率在一百以下,整轮基金就仍是亏损的。从另一方面看,对风投来讲,几十倍的投资回报是完全可及的。上个世纪50年代早期风投AR&DC投资数字设备公司(DEC),回报是5000倍(7万美元到3亿5500万美元),凯鹏华盈和红杉资本投资Google是500倍(1000万美元到50亿美元),而Google的第一个天使投资人安迪·贝托谢姆的回报超过万倍(10万美元到2012年4月的20亿美元)。
要做到高回报,首先必须选对题目。一个好的创业题目最要紧的是具有新颖性,通常是别人没想到的,而不是别人已经做成功的。很多创业者喜欢模仿,易然这样也有成功的可能,却不可能为风投挣到几十上百倍的投资回报。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了很多做DVD机的厂家,早期的几家挣到了钱,后面的几百家都没挣到什么钱;其次,创业的题目不能和主流公司的主要业务撞车。上个世纪90年代时,风投公司对软件公司的创业者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要做的事情,微软有没有可能做?”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如果回答“可能”,那么风投基金的总合伙人接下来就会说,“既然微软会做,你们就不必做了”。如果回答是“不会”,那么总合伙人又会说,“既然微软不做,看来没必要做,你们做它干什么”。2000年后,风投公司还是向软件和互联网的创业者问这个问题,只是微软变成了Google。这个例子说明,如果创业的项目与微软和Google这类公司的业务有可能撞车,那么失败的可能性极大。
除此之外,一个好的题目还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 这个项目一旦做成,要有现成的市场,而且容易横向扩展(Leverage)。
这里面要说几句“现成市场”的重要性,因为一个新兴公司不可能等好几年时间,等市场培育成熟才开始销售。事实上有很多失败的例子是技术、产品都很好,但市场条件不成熟。比如当年甲骨文搞的网络PC,从创意到产品都不错,但是当时既没有普及高速上网,更没有强大的数据中心,最终失败了。直到10多年后,Google提出“云计算”的概念并建立了全球相联的超级数据中心,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的这个梦想才可能成为现实。但是,没有一个小公司等得起10年。
横向扩展是指产品一旦做出来,很容易低成本地复制并扩展到相关领域。微软的技术就很好横向扩展,一个软件做成了,想复制多少份就复制多少份。太阳能光电转换的硅片就无法横向扩展,因为它要用到制造半导体芯片的设备,成本很高。目前太阳能硅片是利用半导体制造的剩余产能生产的,而这剩余产能的规模是不可能无限制扩大的。
- 今后的商业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会以几何级数增长。
我们前面介绍的手机软件的项目就不具备这个特点,因为它的增长被手机的增长限制死了。
- 必须具有革命性。
我通常把科技进步和新的商业模式分成进化(Evolution)和革命(Revolution)两种,易然两者的英文单词只差一个字母,意义可差远了。创业必须有革命性的技术或商业模式。
现在,让我们看一个好的例子—一PayPal,它具备上述好题目所必需的条件。首先,它的市场非常大。世界上每年的商业交易额在数十万亿美元,其中现金交易占了将近一半,信用卡占1/4;其次,它的市场条件成熟了。随着网上交易的发展,现金和支票交易显然不现实,只能倬用信用卡,其交易方式如图15.1所示。
图15.1 一般信用卡交易方式
而信用卡在网上使用经常发生被盗事件(比如商家是钓鱼的奸商,一旦获得买家信用卡信息,就会滥用其信用卡),安全性有问题。因此,需要一种方便的网上支付方式。
PayPal的想法很好,由它来统一管理所有人的信用卡或银行账号,商家不能直接得到买家的账号信息。交易时,商家将交易的内容告知PayPal,并通过PayPal向买家要钱,买家确认后,授权PayPal将货款交给商家,商家无法得知买家信用卡和银行账户信息。而目,PayPal要求商家和买家提供并确认真实的地址和身份,尽量避免欺诈行为。对于500美元以下的交易,PayPal为付款方提供保险,如果付款方被骗,PayPal将偿还付款方损失,由它去追款。PayPal的商业模式如图15.2所示。
这种付款方式要安全得多,好处显而易见,在网上购物的发展起来后,便具备了推广条件,不需要培养市场。而每年十几万亿美元的交易,对PayPal来说几乎是无穷大的发展空间。尽管2009年PayPal已经有700亿美元左右的交易额,但是现在仍以20%以上的高速度发展,和10万亿美元的市场相比,发展空间依然很大。所以PayPal这个题目是一个可以在很长时间内高速发展的生意。PayPal在技术上虽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商业模式却是革命性的。和PayPal类似的,还有中国阿里巴巴公司的支付宝。
图15.2 PayPal信用卡交易方式
风投公司一旦确定什么生意、什么公司可以投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估价一家投资对象了。和投资股市不同,风险投资的对象大多没有利润,甚至没有营业额可言,其估价不能按照传统的市盈率(P/E值)或折扣现金流(Discounted Cash Flow)来衡量,关键是看该公司未来几年的发展前景以及目前为止该公司发展到哪一步了。和投资股市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新创公司因为没有什么业绩可以衡量,创始人和早期员工的素质就变得很关键。一般来讲,一些高资质(High Profile)的创始人,比如思科公司的资深雇员和斯坦福的教授创办的公司容易获得较高的估价。
将资金投人一个新创公司后,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才刚刚开始。
5 风险投资就是投人
威廉·德雷帕(William Draper)是世界上第一批专职风险投资人,他一生并没有投出太多的本垒打,即回报在50倍以上的明星公司,却被后辈尊为风险投资的教父之一,原因在于他确立了很多风险投资的铁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风险投资就是投人。而对于天使投资来说,“创始人靠谱”几乎是决定投资与否的唯一标准,因为创业公司的其他方面在那么早的阶段还很难衡量。
按照德雷帕的理论,一个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本身远比他们所要做的项目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流的人有可能把二流的项目做成一流,而二流的人即倬有幸遇到一流的项目,也一定会把它做成二流甚至三流的。因此,很多风险投资公司在做决策时,先要考察(或者调查)创始人是否靠谱,然后听他们说要做的项目。除了上述这条根本性的原因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了解投资人的重要性。
首先,一家创业公司最后失败是常态,成功都是特例。在2005—2014年的十年时间里,硅谷地区有案可查的获得投资的公司每年大约有4000家,而上市的公司每年只有100家左右,只占到创业公司的2%——3%左右。并购的案例每年大约1000例,但并不是所有的并购都能带来投资回报,即使把所有并购都算成有投资回报,投资成功的比例依然只有1/4左右。那些成功上市或者被并购的公司,无一例外都要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即使在外界看来一帆风顺,但是内部人都深知道路之崎岖。在这艰辛而漫长的成功道路上,创始人或者高层管理团队需要做出很多次的抉择,任何一次错误的抉择都会导致失败的结果。在每一次抉择时,创始人的见识、领导力和判断力(还有运气)就显得特别重要。如果一个创始人能够在前后四五次甚至更多的抉择时都选择正确,必定有过人之处。因此,投资人最重要的是找到那些能在关键时刻引导公司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人。如果创始人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对于那些好项目,后期的风险投资人可能会要求更换CEO后再投资,而天使投资人则宁可不投。
其次,对于天使投资基金来说,它们所投的项目因为太早期,既没有利润,也没有收人,甚至没有几个用户,坦率地说再有经验的投资人在这个阶段也很难看准项目本身能否成功,撞大运的成分居多。如果创始人的专业素养和能力都比较高,他们找的项目可能就比较靠谱。反之,如果创始人本身水平较差,他们能够找到好项目的可能性就非常低。风险投资本身是一件不确定的事情,其回报好坏其实就是比成功率,投资给相对更优秀的人,成功率必然高。
第三,大部分创业成功的公司,最后做成功的事情和他们最初找天使投资想做的事情通常不是一回事,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公司的主营方向可能已经改变了好几次。Google公司最初想通过做企业级的搜索服务挣钱,做的一直非常辛苦却未能盈利,最后找到了在线广告的途径才成为今天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公司。Facebook最早是想通过发展名牌大学用户走高端路线,因而发展缓慢,后来改成了走草根路线并打造开放平台才做到了指数级增长。至于为什么这种不断的变化是创业公司成功的常态,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毕竟IT领域的技术和市场变化都太快,以至于难以在一开始就把今后几年要做的事情完全规划好,大部分成功的公司不是规划得更好或者项目更好,而是更能适应变化。当然,迎接变化和挑战主要靠公司的创始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诚信是成功的关键,这对于创始人如此,对于风险投资更是如此。对风险投资人来讲,最重要的是投资给那些恪守合同,把投资人的利益和自身利益一同考虑的创始人,而不是想尽办法坑骗投资人资金的投机者。在投资人看来,创始人的“德行”比能力来得更重要,比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更为重要了。为了确保投资人的利益,风险投资基金常常要对创始人和创始团队进行细致的背景调查,以免投资被骗,这在天使投资阶段更是如此。不过即便如此,风险投资被骗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
在天使投资阶段,项目的不确定性太大,唯一确定的就是创始人本身了。因此,对于天使投资来说,投资其实就是对一个创始人的选择。一些天使投资人看好了某些创业者,随便他们做什么项目,只要不是太离谱的项目,都会投资。
6 风投的角色
对风险投资家来讲,最理想的情况是能当一个甩手掌柜:把钱投到一家公司,不闻不问,几年后拿回几十倍的利润。对于天使投资和早期投资,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比如有家南非的投资机构Naspers,到中国后两眼一抹黑不知道该投谁,于是就找到了一家美国的咨询公司做顾问。这家咨询公司里有一位二十多岁来自美国加州的小伙子大卫·沃勒斯坦(David Wallerstein)建议Naspers投资腾讯,因为它每天的流量很大。Naspers听从沃勒斯坦的建议投资腾讯后,沃勒斯坦本人却跑回了美国,后来干脆加入了腾讯Naspers找不到沃勒斯坦,公司里也没有能讲中文可以跟腾讯公司沟通的人,便任由腾讯自己折腾。等腾讯上市时,这笔投资已经挣了几十倍的利润。今天Naspers依然占腾讯31%的股份(2019年初),投资回报超过3000倍,当然这也和腾讯恪守诚信,从不随意稀释投资人的股份,也不悄悄转移资产有关。对于绝大多数规模比较大的风险投资,这种情况反而很少发生。大多数创业者的经验总有局限性,尤其是IT行业的创始人大多技术出身,没有商业经验和“门路”(在美国,门路和在中国一样重要)。风投公司就必须帮助那些创始人把自己投资的公司办好。毕竟,他们已经在一条船上了。
风投公司介人一个新兴公司后的第一个角色就是做顾问。这个顾问不仅需要在大方向,比如商业上给予建议,而且还要在很多小的方面帮助创始人少走弯路。我在第13章“硅谷奇迹探秘”中提到,创办一个小公司会遇到形形色色的问题,而创始人常常缺乏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这时风投公司(坐在被投公司董事会席上的那个人)就必须帮忙了。我的一位朋友原来是苹果公司副总裁、乔布斯的朋友,现在是活跃的投资人,他给我讲了下面一个故事。留心各大公司图标(Logo)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几乎所有大公司的标志和名称字体都是采用单色的设计,尤其是20多年前。至今很少有公司像Google那样倬用明暗分明的彩色标志。我的这位朋友告诉我,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彩色印刷比单色(和套色,比如普通黑字套蓝色)印刷要贵得多,公司初创,必须本着能省一点是一点的原则,如果一家公司所有的文件和名片都采用彩色印刷,办公成本将增加;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所有的传真机和绝大部分复印件都是黑白的,印有彩色标志的公司传真不仅不可能像原来彩色的那样好看,而目有些颜色可能还印不清楚。这样不仅让商业伙伴分辨不清,还不容易给客户留下深刻印象。他告诉我,很多年轻的创始人喜欢为自己公司设计漂亮的彩色标志,实际宣传效果并不好。
当然,上面只是一个小的例子。风投介入一个新兴公司后,可以帮助创业者少走很多弯路,总的来说好的风投是创业者的好伙伴。
当然,风投不可能替公司管理日常事务。这就有必要替公司找一个职业经理人来做CEO(当然,如果风投公司觉得某个创始人有希望成为CEO,一般会同意创始人兼CEO的职位)。每个风投基金投资的公司都有十几到几十家,要找到几十个CEO也并非易事。因此,有影响的老牌风投公司实际上手里总攥着一把CEO候选人。这些人要么是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要么是该风投公司以前投资过的公司创始人和执行官。风险投资家给有能力的创始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锁定和他的长期关系。如果后者创业成功固然好,万一失败了,风投资本家在合适的时候会把他派到自己投资的公司,掌管该公司日常事务。一个风投公司要想成功,光有资金、有眼光还很不够,还要储备许多能代表自己管理公司的人才。这也是著名风险投资公司比小投资公司容易成功的原因之一,前者手中攥着更多更好的管理人才。
风投公司首先会帮助被投资的公司开展业务。自己开公司的人都知道,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公司向大客户推销产品时,可能摸不对门路。这时,“联系”广泛的风投公司会帮自己投资的小公司牵线搭桥。越是大的风险投资公司越容易做到这一点。风投公司还会为小公司请来非常成功的销售人才,这些人靠无名小公司创始人的面子是请不来的。风投广泛的关系网对小公司更大的帮助是,它们还会帮助小公司找到买主(下家)。这对于那些不可能上市的公司尤其重要。比如,KPCB早期成功投资太阳公司后,就一直在太阳公司的董事会里,利用这个便利,KPCB将后来投的很多小公司卖给了太阳,这些小公司对太阳是否有用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投资者的钱是收回来了,创业者的努力也得到了客观的回报。在这一类未上市公司的收购案中,最著名的当属Google收购YouTube一事。两家公司都是由红杉资本投资,著名投资人莫里茨同时担任两家公司的董事。YouTube能成功地卖给Google,红杉资本作用不小。风投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越是成功的风投公司,投资公司成功上市的越多,它们以后投资的公司相对越容易上市,再不济也容易被收购。因此,大多数想去小公司发财的人,选择公司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看它幕后风投公司的知名度。Google很早就已经是求职者眼中的热门公司了,固然有它许多成功之处和吸引人的办法,以及创始人的魅力,但是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在于它是第一家KPCB和红杉资本在同一轮一起投资的公司,在此以前,这两家风投从不同时投一家公司。
风投是新兴公司的朋友和帮手,因为它们和创始人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通常也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任何一家公司的创办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一个被投公司前景不妙时,如果投资者处于控股地位,可能会选择马上关闭或贱卖该公司,以免血本无归。这样,创始人就白忙了一场,一定会倾向于继续挺下去,这时就看谁控制的股权,更准确地讲是投票权(Voting Power)多了。当一家公司盈利有了起色时,风投会倾向于立即上市收回投资,而一些创始人则希望将公司做得更大后再上市。投资人和创始人闹得不欢而散的情况也时常发生,投资人甚至会威胁赶走创始人。
创业者和投资者的关系对于成功的创业至关重要。首先,创始人总是在前台扮演着主角,风投在幕后是辅助者。如果投资者站到了前台,要么说明创始人太无能,要么说明投资人手伸得太长,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公司都办不好;其次,创业者和投资者的关系是长期的,甚至是一辈子的。对投资者来讲,投资的另一个目的是发现并招揽人才。对投资人来讲,创业者能一次成功当然是最好的,但是,非常有能力的创始人也会因为时运不济而失败,这时投资者如果认定创始人是个人才,将来还会投资他的其他项目,或者将他派到新的公司去掌舵。因此,对创业者来讲,易然风险投资的钱不需要偿还,但是,拿了投资者的钱就必须使出吃奶的力气把公司做好,以获得投资者的青睐。一些短视的创业者把风投公司当作一次性免费提款机,只拿钱而不承担应尽的义务,实际上等于断了自己的后路。和很多行业不同,不同风投公司的投资家一般会经常䶼通消息,一个人一旦在风投圈子里失去了信用,基本上一辈子就不再可能获得风投资金再创业了。
7 著名的风投
就像华尔街已经等同于美国金融业一样,在创业者眼里“沙丘路”(Sand Hill Road)便是风险投资公司的代名词。沙丘路位于硅谷北部的门罗帕克(Menlo Park),斯坦福大学向北一个高速路的出口处(图15.3)。
图15.3 著名的沙丘路
沙丘路只有两三公里长,却聚集了十几家大型风险投资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技公司至少有一半是由这条街上的风险投资公司投资的。其中最著名的包括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凯鹏华盈(Kleiner,Perkins,Caufield &Byers,简称KPCB或KP)、NEA(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新企业联合公司)、Mayfield,等等。NEA易然诞生于美国“古城”巴尔的摩,但经营活动主要在硅谷,它投资了约500家公司,其中三分之一上市,三分之一被收购,投资成功率远远高于同行。它同时是中国的北极光创投的后备公司(Backing Company)。Mayfield是最早的风险投资公司之一,它的传奇之处在于成功投资了世界上最大的两家生物公司:基因泰克(Genentech)和安进(Amgen),这两家公司占全球生物公司总市值的一半左右。除此之外,它还成功投资了康柏、3Com、SGI和SanDisk等科技公司。而所有风投公司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便是红杉资本和凯鹏华盈了。
7.1 红杉资本
Sequoia是加州的一种红杉树,它是地球上最大的(可能也是最长寿的)生物。这种红杉树可以高达100米,直径8米,寿命长达2000多年。1972年,投资家唐·瓦伦丁(Don Valentine)在硅谷创立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以加州特有的红杉树命名,即Sequoia Capital。该公司进人中国后,取名红杉资本。
红杉资本是迄今为止最大、最成功的风险投资公司。它投资成功的公司占整个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市值的1/10以上,包括苹果、Google、思科、甲骨文、雅虎、网景(1999年被美国在线收购)和YouTube(Google旗下,未上市)等IT巨头和知名公司。它在美国、中国、印度和以色列有大约50名合伙人,包括公司的创始人瓦伦丁和因为成功投资Google而被评为最成功投资人的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
红杉资本的投资对象覆盖各个发展阶段的未上市公司,从开创期到即将上市的公司。红杉资本内部将这些公司按发展阶段分成三类。
种子孵化阶段(Seed Stage)的公司。这种公司通常只有几个创始人和一些发明,要做的东西还没有做出来,有时公司还没有成立,处于天使投资人投资的阶段。红杉资本投资思科时,思科就处于这个阶段,产品还没搞出来。
早期阶段(Early Stage)的公司。这种公司通常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概念和技术,并做出了产品,但是在商业上还没有成功。当初它投资Google时,Google就处于这个阶段。当时Google.com已经有不少流量了,但是还没有挣钱。
发展阶段(Growth Stage)的公司。这时公司已经有了营业额,甚至有了利润,但是,为了发展,还需要更多的资金。这个阶段的投资属于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红杉资本在每个阶段的投资额差一个数量级,分别为10万一一100万美元、100万—1000万美元和1000万一5000万美元。
相比其他风投公司,红杉资本更喜欢投快速发展的公司(而不是快速盈利的),尽管风险较大。苹果、Google、雅虎等公司都具备这个特点。那么如何判定一家公司有无发展潜力呢?据我了解,红杉资本大致有两个标准。
第一,被投公司的技术必须有跳变(用红杉资本自己的话讲叫做Sudden Change),就是我常说的质变或革命。当然,如何判断一项技术是真的革命性进步还只是一般的革新,需要有专业人士帮助把关。红杉资本名气大,联系广,很容易找到很好的专家。
第二,被投公司最好处在一个别人没有尝试过的行业,即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比如在苹果以前,个人电脑行业一片空白;在雅虎以前,互联网还没有门户网站。这样的投资方式风险很大,因为还没有人证明新的领域有商业潜力,当然做成了回报也高。这种投资要求总合伙人的眼光要很准。相对来说,红杉资本的合伙人经历的事情较多,眼光是不错的。
对于想找投资的新创业公司,红杉资本有一些基本要求。
- 公司的业务几句话就能讲清楚。红杉资本的投资人会给你一张名片,看你能不能在名片背面空白处写清楚。显然,连创始人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业务将来也很难向别人推销。
- 就像我前面讲的那样,如果该公司的生意不是10亿美元以上的生意,创业者就不用上门了。
- 公司的项目(发明、产品)带给客户的好处必须一目了然。
- 要有绝活,也即核心竞争力。
- 公司的业务是花小钱就能做成大生意的。比如说当初投资思科,是因为它不必雇多少人就能搞定路由器的设计。要让红杉资本投资一家钢铁厂,它是绝对不干的。
对于创始人,红杉资本也有一些基本要求。
思路开阔,脑瓜灵活,能证明自己比对手强。
公司和创始人的基因要好。当然这里不是指生物基因。红杉资本认为,一家公司的基因在成立的三个月中形成,优秀的创始人才能吸引优秀的团队,优秀的团队才能奠定好的公司基础。
动作快,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打败现有的大公司。刚刚创办的小公司和跨国公司竞争无异于婴儿和巨人交战,要想赢必须快速灵活。
有志创业的读者可从红杉资本的网站(http://www.bei.sequoiacap.cn/zh/contact.html)找到相应的联系方式。
在联系红杉资本之前,创业者要准备好一份材料,包括:
- 公司目的(一句话讲清楚);
- 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尤其要说清楚该方法对用户有什么好处;
- 要分析为什么现在创业,即证明市场已经成熟;
- 市场规模,再强调一遍,没有10亿美元市场的公司不要找红杉;
- 对手分析,必须知己知彼;
- 产品及开发计划;
- 商业模式,至关重要;
- 创始人及团队介绍,如果创始人背景不够强,可以拉上一些名人做董事;
-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想要多少钱,为什么,怎么花。
7.2 凯鹏华盈(KPCB)
在风投行业,能与红杉资本分庭抗礼的只有同是在1972年成立的KPCB了。KPCB取自四个创始人Kleiner、Perkins、Caufield和Byers名字的首字母。虽然它在中国不是很有名,投资也不算很成功,但是在硅谷它甚至有超过红杉资本之势。
凯鹏华盈成功投资了太阳公司、美国在线、康柏电脑、基因泰克、Google、eBay、亚马逊(Amazon)和网景等著名公司。它投资的科技公司占纳斯达克前100家的1/10。KPCB投资效率之高让人膛目结舌。它最成功的投资包括:
- 1999年,以每股约0.5美元向Google投资1 250万美元,回报近千倍;
- 1994年,投资网景400万美元获得其25%的股权,回报250倍(以网景公司卖给美国在线的价钱计算);
- 1997年,向Cerent投资800万美元,仅两年后当思科收购Cerent时这笔投资获利20亿美元,也即250倍,这可能也是它收回大规模投资最快的一次;
- 1996年,向Amazon投资800万美元,获得12%的股权,回报达两三百倍。
它早期成功的投资,包括对太阳公司和康柏电脑等公司的投资回报率均不低于上述案例,只是美国证监会没有提供在线的记录,无法计算那些投资的准确回报。从这些成功投资的案例可以看出,风投公司追求50倍的回报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凯鹏华盈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合伙人知名度极高,人脉极广,除了活跃的投资人约翰·杜尔和布鲁克·拜尔斯(Brook Byers,KPCB中的B),还包括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前国务卿鲍威尔和太阳公司的共同创始人比尔·乔伊等人。凯鹏华盈利用其在政府和工业界的影响,培养新的产业。比如鉴于戈尔同时担任了苹果公司的董事,凯鹏华盈专门设立了一项培育iPhone软件开发公司的基金,规模为一亿美元。考虑到今后全球对绿色能源的需求,凯鹏华盈又支持戈尔担任主席的投资绿色能源的基金,并集资4亿美元成立专门的基金。凯鹏华盈通过这种方式,在美国政府制定能源政策时施加影响。
除了绿色能源外,凯鹏华盈主要的投资集中在IT和生命科学领域。在IT领域,凯鹏华盈将重点放在以下6个方向:
- 通信;
- 消费者产品(比如网络社区);
- 企业级产品(比如企业数据管理);
- 信息安全;
- 半导体;
- 无线通信。
想创业的读者可以从中找找好的创业题目。
凯鹏华盈并非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却是长期以来做得最成功的。据凯鹏华盈的一位合伙人讲,他们通常将每一轮基金的规模控制在8亿一10亿美元,在杜尔等人看来,风险投资是投未来的新技术,规模不会太大,并不需要太多的钱。基金的规模太大,除了投资时大手大脚,没有更多的好处。从上个世纪70年代该基金成立至今(2015年),它一共融资大约20轮,筹措的资金不到200亿美元,但是它返还给投资人的钱却高达8000亿左右,也就是说,每一轮基金的平均回报为40倍。在风险投资上,一两次做到高回报并不难,难的是40多年几代投资人一直能维持这样稳定的回报。至于凯鹏华盈的投资秘诀是什么,除了遵守纪律,就是只投资那些可能改变世界的项目。关于这一点,我在得到专栏《谷歌方法论》中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虽然凯鹏华盈在硅谷名气很大,但它依然保留着“礼贤下士”的好传统。凯鹏华盈的合伙人,包括杜尔,经常去斯坦福大学的“投资角”参加研讨会。杜尔对年轻的创业者保证,他一定会读这些创业者写给他的创业计划书和E-mail,尽管可能没有时间一一回复。凯鹏华盈对创业者的要求和红杉资本差不多,要找凯鹏华盈的准备工作也和找红杉资本相似,这里不再重复。
最后补充一点,除了红杉资本和凯鹏华盈,日本的软银集团(SoftBank)是亚洲最著名的风投公司,它成功地投资了雅虎和阿里巴巴,并目控股日本雅虎。IDG资本虽然在美国没有太大的名气,但是它最早进人中国市场,在中国反而比红杉资本和凯鹏华盈成功。另外,俄罗斯的DST近几年在世界上也非常活跃,它最著名的投资是在2010年投资了Facebook公司。
7.3 创新工场
在世界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中,李开复领导的创新工场是无论如何排不进前列的。它起步晚,融资规模也较小,而目投资或孵化的公司至今也没有一家上市。但是它很有特色,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创造了相当正向的社会效益,因此我将它列入本书。
中国一般的读者对创新工场的了解恐怕远比前面提到的凯鹏华盈和红杉资本要多得多。(因此它的细节和故事这里也就不多说了。)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李开复的个人魅力。与中国其他风险投资或者天使投资大多是仿照美国同行的做法不同,创新工场在美国没有可对比的对象,可以讲完全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大学生(包括研究生)毕业创业的欲望和行动远不如美国的大学生。这里面原因很多,比如中国大学生的社会成熟度和自立能力远不如美国的同龄人,从小应试教育导致创造力和想象力贫乏,等等。但是还有两条原因与社会因素有关。首先,中国鲜有天使投资人。中国的风险投资大多注重短期效益,显然做上市前最后一两轮投资比从第一轮就开始投要见效快很多,甚至很多风险投资最后蜕变成私募基金,并没有扶植刚刚起步的新技术。另一方面,中国富有的个人或家庭,虽然在投资房地产和消费上早就超过了美国的富豪,但是很少有人会去做天使投资人。这样一来,刚毕业的大学生想创业,很难得到风险投资或者天使投资的帮助。第二,在中国注册一个公司比在美国麻烦得多,即使注册下来,伺候众多婆婆(各级主管)也要消耗巨大的精力,刚刚创业的年轻人被迫“不务正业”,要花很大精力搞定这些业务以外的事情。易然也有像浦东软件园和苏州科技园那样主动帮助创业者排忧解难的政府部门,但是在全国大部分城市,相关部门不太会关注暂时看不到GDP的创业小公司。这样,大部分大学生也就“知难而退”,毕业后进入收入稳定的大公司打工。
创新工场的作用在于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年轻人解决了这两个问题。首先,它愿意帮助有想法的年轻人开展自己的项目(第一步还谈不上成立公司),并为这些团队提供场地和基本工资。第二,它会提供法务、财务等创业相关服务,帮助创业团队解决了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难题,倬年轻人可以专注于他们的创业。这两点大大降低了年轻人创业的门槛。
当然,年轻人获得这些好处的同时也要付出代价。首先是经济上的代价,即创新工场要占这些项目(未来可能是公司)相当比例的股权。我们前面说过,资本越早进入创业阶段,股权占比越大。从资本进入时间来讲,没有比创新工场的模式更早的了。如果统计一下创新工场剥离的那些融到风险投资资本的小公司,大家会发现创新工场早期提供的那些服务其实是相当昂贵的。这个结果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创始团队在今后的公司中可能没有太多股份了,因此创业的动力远没有那些在居民楼里租两个单元房创业的人高。我看了一家从创新工场剥离出来的颇为有名的公司,据说大部分员工晚上九十点钟也就回家了,和Google或者Facebook早期夜以继日地创业简直没法比。其次,经济上的代价一定会带来主导权的代价,很多创业公司经过一两轮融资后创始人就已经丧失了对公司的控制权,而从创新工场分出来的公司更是如此。
由于赶上了2011年中国的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的热潮,创新工场到目前融资很顺利,并目成功地将一些项目剥离出去,变成独立的公司,而且这些公司的估价并不低。但是毕竟它运作的时间太短,还没有一家孵化的公司上市,从投资收益的角度看还远没有成功。按照创新公司正常的淘汰率计算,这些被孵化的公司很多不会很成功,因此到创新工场试水的年轻人第一次创业的努力很可能是以失败告终。即便如此,创新工场的社会效益并不会因此而降低。
创新工场的社会效益体现在这样几方面。首先,它培养了一大批勇于创业的年轻人,虽然他们第一次创业极可能失败,但获得了第一手的创业经验,将来自己第二次、第三次创业(或许不再需要创新工场)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同时客观上会鼓励更多大学生加人到创业大军中。第二,创新工场的出现,或许是因为李开复个人的魅力和社会活动本领,倬得中国整个投资领域,甚至整个社会开始关注天使投资。有了全社会的关注和更多资本的引人,中国的天使投资和年轻人的创造力将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这对整个中国的科技进步有非常大的好处。
创新工场是在中国特定商业环境和投资环境下产生的特殊的天使投资方式,就连李开复自己都说,如果他在美国做天使投资一定不会采用这种方式。但是在中国现阶段,创新工场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孵化器,它帮助很多年轻人圆了创业梦。
7.4 Y孵化器(Y Combinator)
很难讲Y孵化器属于孵化器还是天使投资,从名称来看它属于孵化器,但是它挣钱又是靠其天使基金,因此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一个特殊的结合体。
Y孵化器由硅谷的创业教父、畅销书《黑客与画家》的作者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创办。格雷厄姆本人是艺术和技术结合的代表人物。他早年在著名的罗德岛设计学院(RISD)学习艺术,该校是北美最好的独立艺术院校,同时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文科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然后他改学理工科并获得了计算机科学的博士学位。格雷厄姆认为科技的发明创造和艺术创作有着相同之处,并且致力于发现富有创造性的年轻人。格雷厄姆做孵化器,或者说做孵化——投资混合体的方式和之前的投资人都不同,他不看重场地等物质条件,而强调人的潜能和经验在创业成功中的重要性。在格雷厄姆看来,找到有潜能的年轻人是成功的第一步,不过这些年轻人未必有经验,因此投资人能够给他们的最大帮助就是提供这种经验。当然,格雷厄姆知道自己的经验有限,便设法聚集了一批有经验的人来帮助他辅导创业的年轻人。
Y孵化器虽然号称孵化器,却没有什么场地,仅有的一点点场地大部分还是小会议室。在那里,Y孵化器对所投公司创始人进行全方位的培训,这种培训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基础的商业知识和技术发展特点,和一般商学院的课程所不同的是,Y孵化器的课程理论性不强,但比较实用。通过这种培训,将创始人从具有某方面特长的人培养成能够经营管理公司的全才。
当然,这样的培训其他机构也能做,Y孵化器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能够为创业者提供特殊的经验和价值。Y孵化器聚集了硅谷很多过去的成功创业者、法务财务专家和企业资深人士。这些人会定期来到Y孵化器,对它旗下的小公司进行全方位的辅导。创业者可以预约这些人的时间,有具体问题可以找那些有经验的“前辈”当面请教。这样一来,Y孵化器的投资成功率比其他的早期风险投资要高不少。从2005年成立到2014年,它的总回报率大约是14—30倍左右,即使按照14倍的下限计算,Y孵化器的投资回报也比整个风险投资行业平均水平高很多。在Y孵化器投资的公司里,最著名的是网上房屋租赁公司Airbnb和云存储公司Dropbox。
在Y孵化器的背后是一些大公司的高管和成功企业家,他们在帮助Y孵化器投资的那些公司时,获得Y孵化器给予的报酬,这些报酬当然出自Y孵化器的投资回报。因此,这些成功人士非常有意愿帮助Y孵化器旗下的小公司成长。他们深知自己的公司或者硅谷需要什么技术,并将这些想法不自觉地传递给那些小公司的创始人。这样就让Y孵化器下面的很多小公司有更明确的方向,以便于被大公司收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些新闻:Facebook花高价收购了一些似乎不很知名的小公司,外界常常对这类收购感到很奇怪。其实这些被收购公司的一些投资人和顾问都是Facebook的高管。今天,在硅谷这类间接参与投资的专业人士很多,这些人是连接创业者和潜在收购者的桥梁。
当Y孵化器、创业者和来自大公司的创业导师都得到好处时,大家可能还会问,那些专业人士所在的公司得到了什么好处。它们当然有好处,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它们建立了监控硅谷地区技术和产品动态的雷达网。在硅谷,很多大公司进入新领域靠的是收购小公司,而不是内部开发。这样虽然看上去花的钱比较多,但是却能省时间,在市场上抢占有利位置。Google几项成功的新业务,如Google地图、YouTube和安卓都是靠收购开展起来的,Facebook的图片分享和处理服务Instagram和移动互联网即时通信WhatsApp也是高价收购来的。
Y孵化器的投资方式给硅谷的一些富有的成功人士开拓了投资的新思路,他们很多人通过自愿组合,结成天使投资团体,在给创业者提供资金的同时,更多地给创业者以辅导。在世界各地,资金相对容易获得,而有经验的专业人士数量则有限,今天常常是投资人的智力、经验和人脉,而不是资金,决定了一个小公司的成败。Y孵化器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最有效地调动了硅谷地区的智力和经验。
2018年,前微软高级副总裁陆奇加人了Y孵化器,主管其中国业务,IT行业很多人对于这家颇具传奇色彩的孵化器在中国如何发展充满了好奇,而这要看陆奇如何打造中国的团队了。
结束语
易然风险投资的目的是追求高利润,但这些高利润是它们应得的报酬。我对风险投资家的敬意远远高于对华尔街的,因为风险投资对社会有很大的正面影响,而华尔街经常会起负面作用(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油价暴涨暴跌很大程度上是由华尔街造成的)。风险投资通常是为创业者雪中送炭,不管创业成功与否,它们都在促进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更新。而华尔街许多时候只是将一个口袋里的钱放进另一个口袋里,并从中攫取巨额财富。
风险投资者是创业者幕后的帮手,但是他们无法代替创业者到前台去经营。创业的关键还在创业者自己。
第16章 信息产业的规律性
1 70–20–10律
2 诺威格定律
3 基因决定定律
结束语
在新的信息技术产业刚刚形成时,总会有多个可以䶼相抗衡的竞争者。但是,一旦有一家主导公司出现,它就可能成为该行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继而在商业上拥有不可估量的优势,并迅速占领全球市场。在信息产业,这个过程通常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但是,一旦一家公司占有全球一大半的市场,它就不得不寻找新的增长点。而这时的跨国公司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朝气蓬勃的公司了,固有的基因令它转型十分艰难,若能幸运地成功转型,它将再次获得新生,否则就会被技术革命的浪潮淘汰。
科学技术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一次次技术革命的浪潮造就出浪尖上的成功者,淘汰掉赶不上大潮的失败者。当一些人还在为那些曾经伟大的公司的消亡感到可惜的时候,我想说的是,任何过气公司退出历史舞台,是它们对世界做的最后一次贡献,唯有如此,才会有更多的资源分配给新的公司、新的行业。
第17章 硅谷的摇篮 斯坦福大学
硅谷的兴起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斯坦福大学多方位的支持。IT领域的很多大公司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创办的,包括惠普、思科、雅虎、Google、英特尔、太阳公司、制造处理器和工作站的MIPS和SGI公司、世界最大的GPU公司NVIDIA、世界最大的视频电话会议公司WebEx、最新潮的社交网络Snapchat等,另外在非科技领域还有著名的耐克(Nike)公司。此外,微软前CEO史蒂夫·鲍尔默和董事会共同主席吉姆·阿尔钦也在斯坦福读过书斯坦福在商业界和科技界创下的这种奇迹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流大学都不能比的。为什么斯坦福大学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呢?这要从它的发展、它的文化说起。
1 传奇大学
关于斯坦福大学的各种传奇故事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有些是真的,有些是杜撰的。其中流毒最深远的讹传是这样的:
有两个“乡巴佬”夫妇,找到哈佛大学,提出为哈佛捐一栋大楼。哈佛大学的校长很傲慢地说,捐一栋楼要一百万,然后三句两句便把这对老夫妇打发走了。这对老夫妇一边走一边唠叨,才一百万,才一百万。他们有一个亿要捐,于是干脆自己捐了一所大学,就是今天的斯坦福大学。
这个讹传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广为流传,以至于斯坦福大学不得不在官方网站上辟谣。其实,这个讹传漏洞很多。首先,了解斯坦福大学历史的人都知道老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 Sr.)可不是一般的人,绝不是什么乡巴佬。他不仅是加州的铁路大王,还担任过加州州长、美国联邦参议员,属于精英阶层(Elite Class),他甚至还是林肯总统在美国西部重要的政治盟友。我们在后面还会介绍到他的夫人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第二,在19世纪,一亿美元是一个天文数字,100万美元也是一大笔财富。美国以前最大的银行花旗银行到20世纪30年代,存款才达到几千万美元。截至斯坦福大学创办的20年前,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捐赠不过700万美元,用于创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霍普金斯医学院。在老斯坦福的捐款中,现金只有1000多万美元,这已经是当时美国最大的捐款了。老斯坦福的捐赠中最值钱的是33平方公里(8000多英亩)的土地。当年加州属于“蛮夷之地”,土地值不了多少钱,但是今天斯坦福所处的帕洛阿尔托市是世界上土地最贵的地方之一,这些土地的地价涨了不止万倍,因此斯坦福也成为了今天实际资产最多的大学。第三,哈佛大学和美国所有的大学对捐助者从来都是非常殷勤的。坦率地讲,它们比中国的大学要殷勤得多,不会怠慢任何慈善家。这是美国大学能得到巨额捐助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并流传前面那么荒唐的谎言,原因有三。首先,可能是哈佛大学当年校长艾略特的儿子杜撰了这个谎言,这是目前通行的解释。其次,这个谎言多少符合一些逻辑并且容易给人以传奇的感觉。最后,不得不说世界上有不少人缺乏常识和思考,并目热衷于传播谣言。
关于斯坦福大学,真实的故事是这样的:老利兰·斯坦福夫妇把他们唯一的孩子小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 Jr.)送到欧洲旅行,为日后在那里读书做准备,结果他们的孩子不幸在欧洲去世。斯坦福夫妇很伤心,后来决定用全部的财富(大约几千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0亿美元)为全加州的孩子(而不是传说中的全美国或全世界的孩子)做点事情,他们曾经考虑过各种慈善的形式,比如创办一些医院,等等,最后在一些美国东部大学校长,包括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的建议下,决定建立一所大学,纪念他们自己的孩子。这所大学被命名为小利兰·斯坦福大学(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简称斯坦福大学。
图17.1 斯坦福大学纪念教堂前的走廊上,为每届学生安放了一个永久性的纪念铜牌
1885年斯坦福大学注册成立,两年后举行了奠基仪式,1891年开始正式招收学生。当时一共有约500名学生(包括很多插班生),只有15名教授,其中一半来自康奈尔大学。在这首批学生中,产生了一位后来美国的总统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就是那位被评为最差的、把美国带进1929—1933年大萧条的总统。但是斯坦福仍然很为他感到自豪,并建立了著名的胡佛研究中心)。易然斯坦福是一所私立大学,但早期不收学费,直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学校财政上难以维持为止。
斯坦福大学的创办过程非常不顺利。斯坦福开课的两年后,老斯坦福便与世长辞了,整个大学的经营和管理重担就落到了他的遗孀简·斯坦福的身上。当时美国经济情况不好,斯坦福夫妇的财产被冻结了。(我估计要么当时美国财产法关于信托财产方面的法律不健全,要么斯坦福夫妇没有把他们的财产转到自己生前信托(Living Trust)下面。这种情况在现在的美国不会发生。)校长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和学校其他顾问建议简·斯坦福关掉斯坦福大学,至少等危机过去再说。这时,简·斯坦福才想到她丈夫生前买了一笔人寿保险,她可以从中每年获得一万美元的年金。这一万美元大抵相当于她以前贵族式生活的开销。简·斯坦福立即开始省吃俭用,将家中的管家和仆人由原来的17人减至3人,每年的开销减少到350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大学教授一家的生活费。她将剩余的近万元全部交给了校长乔丹,用于维持学校的运转。从斯坦福夫人身上我们看到一位真正慈善家的美德。慈善不是在富有以后拿出自己的闲钱来沽名钓誉,更不是以此来为自己做软广告,慈善是在自己哪怕也很困难的时候都在帮助社会的一种善行。
然而,靠斯坦福夫人的年金补贴,学校毕竟不能长期维持下去。于是她亲自到首都华盛顿,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克里夫兰寻求帮助。最终,美国最高法院解冻了斯坦福夫妇在他们铁路公司的资产。斯坦福夫人当即卖掉这些资产,将全部的1100万美元交给了学校的董事会。斯坦福大学早期最艰难的6年终于熬过去了。乔丹校长赞扬道:“这一时期,整个学校的命运完全靠一个善良妇女的爱心来维系。”今天,不仅是几十万斯坦福校友,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感谢斯坦福夫人。她用她的爱心,靠她坚韧不拔的毅力开创出一所改变世界的大学。
关于斯坦福大学的第二个讹传是说斯坦福原来被称作西部的哈佛,后来办得超过了哈佛,结果现在哈佛被称为东部的斯坦福。目不说斯坦福大学有没有全面超过哈佛,作为全球第一知名大学的哈佛大学再不济也不会称自己为东部的斯坦福。同样,心比天高的斯坦福大学根本不以成为什么西部的哈佛而自豪。事实上,斯坦福大学公共关系负责人在接待清华大学代表团时自豪地说,斯坦福大学等于哈佛大学加麻省理工学院(MIT)。虽然这种说法有些狂傲,但是确实有一定道理。
第一,斯坦福大学在专业设置上覆盖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合集。在美国大学里有个普遍的看法(也许是偏见)一一“哈佛的人能写不能算,麻省的人能算不能写”,反映出哈佛侧重文科而麻省侧重理工科(实际上哈佛有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和物理学专业),而斯坦福大学人文理工兼修。在美国,一所大学的综合排名其实没什么意义,关键看专业的好坏。美国最热门的专业首推医学,然后是法律、工程和商业。一个学校的历史专业或政治学专业再好,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影响。斯坦福大学是美国唯一一所在这四大热门专业领域都名列前茅的学校。它的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长期以来并列美国第一,它的法学院仅次于耶鲁大学排在第二,它的工学院仅次于麻省理工排名 第二,斯坦福医学院在美国排名前三。和斯坦福相比,美国其他大学都显得有些“缺胳膊少腿”: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工科很弱,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没有医学院和法学院。
第二,在办学理念上,斯坦福大学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之长于一身。斯坦福大学既强调素质教育,又强调专业教育。事实证明,全面发展有助于斯坦福大学培养出全才,而全才是作为业界领袖的必要条件。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详述这一点。
斯坦福大学的校园被认为是美国三所最美的校园之一(图17.2),另外两所是康奈尔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人从不掩饰对自己学校的自豪感,甚至从教授到学生经常拿其他名校开玩笑。下面是斯坦福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出的一道真实考试题。“某家公司希望设计一种符合A、B、C和D等条件的数字滤波器,他们找到了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说不会,你能帮助他们设计这样的滤波器吗?”我想麻省理工学院的人看了这道考题一定不会舒服。斯坦福人骄傲自有他们的本钱,除了出了众多的实业家,孵化了很多跨国公司,斯坦福大学的学术水平更是闻名于世。到2011年,它有17位在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一半是经济学奖)和几十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毕业生。除此之外,它还有7位获得数学领域最高的终身成就奖(沃尔夫奖)的得主(数学领域的最高奖当属菲尔兹奖,但是它只授予40岁以下的学者,而沃尔夫奖一般授予成就卓著的数学泰斗),4位新闻最高奖普利策奖得主,有150多位美国科学院院士,94多位美国工程院院士和263位美国文理学院院士它的毕业生中不乏在全世界各行各业中执牛耳者。
图17.2 斯坦福大学美丽的校园
在美国众多大学中,建校100多年的斯坦福大学历史谈不上悠久。目不说和有将近400年历史的哈佛大学比,就是和它的邻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斯坦福大学起步也算很晚的。在斯坦福大学诞生后的头50年里,它根本排不进美国一流大学的行列,更不要说和哈佛大学竞争了。到二战后,斯坦福大学已经人不敷出,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美国的私立大学完全靠自己筹款,政府并不提供一分钱,再好的私立大学如果经营不善,都可能面临办不下去的危险。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在历史上就出现过非常严重的财政危机,最后是靠它无数事业有成而又关心母校的校友捐助渡过了难关。斯坦福大学当时还没有这么多富有的校友可以依靠,它最大的一笔财富就是斯坦福夫妇留下的33平方公里(8000多英亩)的土地,这超过了澳门的面积,而大学的中心校园占地不到其十分之一(斯坦福大学至今荒地依然多于已倬用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电子工业发展很快,与亚洲的联系比二战前紧密了很多,加州新兴的电子工业和航空工业成为了加州的经济支柱。很多公司有意从斯坦福大学购买土地,但是斯坦福夫妇的遗嘱规定学校永远不得出售土地。这样,斯坦福大学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地荒着而无法发挥作用帮助学校渡过难关。
图17.3 1953年硅谷的第一栋房子
帮助斯坦福大学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它的一位教授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特曼是非常著名的电机工程科学家,担任过斯坦福工学院的院长和教务长,还培养出休利特和帕卡特等优秀弟子,但是他的这些成就大家都记不住了,大家后来只知道他是“硅谷之父”。特曼仔细研究了斯坦福夫妇的遗嘱,发现并未限制大学出租土地,于是他兴奋地声称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秘密武器一一建立斯坦福科技园,科技园向外面的公司出租土地99年。在这99年里租用土地的公司拥有全部倬用权,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建造自己的公司。消息一传出,马上有很多公司表示有兴趣,并很快和学校签署了租约。1953年,第一批公司,包括大名鼎鼎的柯达公司、通用电气、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oratory,后来诞生出集成电路的先驱仙童公司)、洛克希德公司(美国最大的军火商)和惠普公司进驻了斯坦福科技园,图17.3所示的是硅谷的第一栋房子。对斯坦福而言,这件事的影响非常深远,它不仅解决了斯坦福的财政问题,并目成为斯坦福跨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契机。对社会而言,它促成了硅谷的形成。
2 硅谷支柱
美国和其他国家先后出现过很多技术公司聚集地。但是一旦某个或某一批大的公司开始走下坡路,当地的科技发展就开始渐渐落伍。早期的科技公司,比如AT&T和IBM集中在纽约附近,但是在这两家公司之后,不再有这个量级的公司出现。波士顿附近,尤其是128号公路两旁曾经有过一些像DEC那样的大公司和不少颇具发展潜力的公司,但是随着老的公司衰退,新的公司始终不能形成规模。这个地区就很难对世界信息产业产生大的影响。硅谷能够半个世纪长盛不衰,一是得益于亚太经济的发展,二是靠斯坦福等大学不断向硅谷注入新的技术和人才。
很多人奇怪拥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波士顿为什么只能诞生一些小公司,而出不了大的跨国公司。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坦福大学的办学方法和美国东部的名校有很大的不同。斯坦福不是简单地把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专业叠加,从波士顿搬到了加州,而是根据加州的情况办了一所全新的学校。只要既在斯坦福大学,也在美国东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待过一段时间,就能强烈地体会到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
在众多差异中,最重要的是开放性。我这里说的开放性不是指校门24小时开放任人进出,这个要求太低了。美国所有大学,包括西点陆军学院和安纳波利斯(Annapolis)的海军学院都没有围墙,所有参观者可以自由进出。我这里讲的开放性是指一所大学在各方面,从教学到科研、到生活都融人了当地的社区。不论是生活在田园乡村中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还是大都市里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你都能明显感觉到是置身于象牙塔中。在校学生不需要任何交通工具,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和中国大学围墙里的学生一样,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而这些大学里的教授,则是传道、授业、解惑,加上做自己的研究。但是,生活在斯坦福大学,从教授到学生都很难有置身于象牙塔的感觉。
斯坦福大学的这种开放性首先是由生存的需要决定的。斯坦福大学在地域上远离美国的政治中心,导致了它从政府获得的研究经费占整个学校经费的比例远远落后于东部的著名大学。以工学院为例,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规模相当,但是前者获得的政府经费只有后者的一半左右。如果读者仔细研究一下美国顶尖大学的地理位置和政府经费的关系就会发现,大学来自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与它到华盛顿特区的距离成反比。政府资助的研究经费对很多教授来讲并不是很容易申请的。首先要写很长的申请报告,然后通过一轮一轮的评审。在评审过程中,要花很多精力去和经费的主管人员及同行评审人做公关。在美国申请经费,人际关系很重要。一些教授经常请主管经费的自然科学基金会(NSF)、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和国防部(DOD)的主管们参观实验室和参加自己的学术报告会。而这些政府官员们要到斯坦福大学听一次报告并非易事。这样,这些离政府部门近的大学自然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斯坦福大学远在加州,当然就很吃亏。因此,斯坦福大学一些已经提上终身教职并且不缺经费的教授到后来甚至懒得写申请了。
作为大学教授,能从政府拿到大笔研究经费当然是可喜可贺的事。和从工业界拿经费相比,拿政府的经费有很多好处。首先,美国政府的资助一般来讲更充足,在这一点上各国政府都一样,无需额外说明。从美国政府拿科研经费,除非像研制哈勃空间望远镜这类特殊的项目,很少需要做具体的系统,只需要进行方法研究,最后交一份研究报告就可以了。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拿美国政府的研究经费容易交差得多。比如搞语音识别研究,在中国拿了“863”计划的大额经费要做识别系统,而在美国只需要用计算机实现自己的算法,证明其有效即可。很少有教授会像李开复博士那样真正开发一套语音识别系统(美国从来没有中国那样的科研鉴定会)。NSF和DARPA等政府的科研主管机构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教授们因此省去了很多做演示系统的时间和精力,得以将精力完全集中于研究本身。这是美国能够在科技上长期领先于世界,并目几乎每年都有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毫无疑问,很多大学教授乐于接受这样的项目,既能专注做学问、多发表论文,又可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美国大学教授暑假三个月的工资要从自己的科研经费中出)。一些成名已久影响力很大的教授,更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到长期大额的政府合同,比如我在《数学之美》一书中介绍的著名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专家贾里尼克教授便是如此,他的经费常常是系里其他教授经费的总和。久而久之,他们和政府机构之间互相产生了极大的依赖,自己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
但是,凡事有一利就可能有一弊。美国政府的NSF和DARPA等科研经费一般资助的都是工业界不愿意支持的基础研究项目,比如基础科学、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的许多项目。这些研究课题在短期内不可能产生任何商业价值,有些可能永远没有商业价值,由政府出钱来资助这些项目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一旦某个项目具备商业价值,并且可以由公司资助时,政府会渐渐减少并最终停止对这些课题的资助,因为政府(纳税人的代表)认为没有必要和工业界做重复的事,更没有必要和工业界竞争。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日本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美国政府几乎没有资助过搜索技术研究,因为它是一项已经开始盈利的技术。2008年我接待了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参观Google,在最后的提问环节,一位官员问美国是否对Google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扶持和照顾,在场的Google副总裁黄安娜觉得很奇怪,她认为Google作为一家盈利丰厚的公司,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从政府得到特殊的关照。政府需要帮助的是那些不容易盈利的小公司,比如太阳能公司。
即倬是在工程领域,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也常常是非常尖端的,而且可能的应用面非常窄,有时发表的论文都没有几个人真正愿意读,更不用说有商业价值了。贾里尼克教授讽刺这种现象是“除了论文的评审者,没有人会去读这些论文”。美国对政府研究经费管理很严,严厉禁止拿一个项目的经费去资助自己的其他研究项目,即倬经费有结余,教授们也不可能用它来研究有实际应用意义的课题。于是,拿了足够多政府经费的教授通常也就不去研究应用课题了,更不要说自己去开办公司了。久而久之,在美国东部的著名大学里就营造了一种清高的风气,大家比谁获得的政府经费多,谁的研究论文出得多,谁的研究成果理论水平高。教授们的做事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学生。这些学校的博士生们在学校时做实验、写论文,毕业以后接着当教授,或者去大公司的实验室做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拥有美国最好的电机工程系和计算机系,但是麻省理工博士毕业生留校的比例比斯坦福高得多。从做学问的角度讲这完全是对的,但是这种研究对创业帮助不大。
斯坦福大学远离联邦政府,从政府得到的经费比东部的名校少,这也不足为奇。但是,斯坦福大学守着硅谷,从工业界拿的钱比任何一个同样规模的东部大学不知多多少倍。从公司拿钱一般来讲不会有政府那么多,而目还要做很多具体的事。有些公司支持的研究项目甚至无法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所以美国东部名校很多资金充足的教授不屑于和工业界打交道。
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很多。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一起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资金,斯坦福大学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如果只有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与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对于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易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他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遇到问题时找不到解决途径,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大学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公司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麻省理工学院一般是不会碰这种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卡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继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DSL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贝尔实验室早就发明了用于DSL的编码方法,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14.4kbit/s提高到28.8kbit/s费脑筋,做不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年轻助教,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的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DSL的编码方法,并目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Amati公司,真正实现了DSL取代拨号上网这一划时代的变革。
在斯坦福大学,这类例子非常多。大学对教授办公司非常理解和支持。只要一位教授能完成教学任务,并且发表足够多像样的论文,斯坦福并不限制其到外面的公司兼职,甚至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完全离开学校创办公司,或者在公司里担任要职。斯坦福大学第四任校长(2000—2016年)约翰·亨尼西(John Leroy Hennessy)就是最好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他在发明了精简指令集(RISC)处理器MIPS后,便与人合伙创办了MIPS公司。在以后的多年里,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办公司(公司名称就叫MIPS,成立于1984年),而不是在斯坦福大学教学和搞研究。5年后,MIPS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1998年又卖给了它最大的客户SGI公司。这时亨尼西才从工业界抽身出来,回到斯坦福大学担任了工学院院长。经过这一番闯荡,亨尼西成为了难得的管理人才。2000年,他开始担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直到2016年8月底辞去校长一职,由生物学家马克·泰西–拉维尼Marc Tessier-Lavigne继任校长。现在,亨尼西仍是Google和思科的董事,并且在2011年Atheros公司被高通公司收购以前还担任过前者的董事。
开放校园的真正含义在于像斯坦福大学那样,让大学融入社会。开放是斯坦福大学的“本”,而厂校结合是它的“用”。后者保证了大学开放校园的具体实施。
北美很多好的工科大学,比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都强调厂校结合。为了让学生获得工业界的知识,麻省理工学院与AT&T等大公司建立了共同培养学生的计划,进入该计划的学生要在AT&T工作一年(四个暑假),作为回报,AT&T公司支付该学生的学费。美国不少大学有这种类似于奖学金的计划。对于进入这些培养计划的学生而言,这当然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既解决了昂贵的学费问题,又从工业界获得了很好的经验,将来无论是进入工业界,还是继续攻读研究生都大有好处。但是,这种松散的结合对大学和公司的直接帮助都不是很大。对学校来讲,主要的好处不过是大公司替它资助了一些学生,承担了一部分职业教育的义务,但是学生们在公司做的题目和学校通常毫无关系,这种合作对于学校的科研帮助非常有限。对于公司来讲,倒是有了从名牌学校优先选择优秀学生的有利条件,这些学生工作后上手也会比同龄人快些。但是,这些学生,大部分是本科生,毕业以后并不一定会去资助自己的公司工作。在实习期间,他们也根本不可能为公司带来什么新的思想和技术。
斯坦福和硅谷的厂校结合要超出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许多。斯坦福在技术和人才培养上都给予了硅谷公司直接的帮助。在技术上的帮助体现在大量优秀的教授直接到硅谷的公司任职和研究这些公司的科研项目,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在人才培养的帮助上,则首先体现在大学一直在为硅谷各家公司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进行继续教育。硅谷公司多数的工程师并没有硕士学位,不少人在工作中发现自己的专业水平需要提升,斯坦福大学为这些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进修计划,他们可以每学期在大学里修一两门研究生的课程,这样三到五年就能拿到一个硕士学位,有的人甚至一边在公司全职上班,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在斯坦福读博士。易然有时候一个博士学位要读十年八年,但毕竟这也是在全职工作条件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好办法。当然,如果有人不想拿学位只想听一两门课也是可以的。硅谷的公司深知职业培训的重要,一般都会在时间和经济上鼓励员工追求更高的学位。为了方便硅谷员工修课,斯坦福大学有很好的远程教育网络。学生不必到课堂上听课,可以在家里的电视机前上课。斯坦福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通过有线电视向校园和硅谷实时转播,在校学生也没有必要到教室去。很多人一学期未踏进教室一步,照样学得很好。万一上课时间和上班有冲突,在职学生可以在课后到图书馆借出课程的录像补习。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其他大学为周边公司的员工提供了如此方便的职业教育机会。
在斯坦福大学读在职博士的硅谷员工通常比刚刚本科毕业的学生更容易找到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一方面他们有工业界的经历,知道哪些课题今后对自己帮助大;另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需要靠教授的助学金生活,他们更看重教授的研究方向和水平而非研究经费(对于没钱的刚毕业的学生,常常要为了争取奖学金而牺牲自己的兴趣)。世界各国的博士生都面临同样一个问题,花了四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研究的课题毕业以后可能没什么用处,因为博士生不一定能自由选择课题,也未必非常了解学校以外的社会。那些在硅谷工作过的博士生一般就没有这些问题。因此,斯坦福大学在高级人才的培养上效果非常好。
斯坦福大学也为硅谷和工业界培养了很多管理人才。在美国,拥有8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斯坦福商学院与哈佛商学院齐名。硅谷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工作一段时间后会到那里去充电。为了方便日理万机的公司负责人也能到商学院进修MBA课程,除了一般的MBA课程外,斯坦福还提供了专为公司执行官们开设的EMBA课程。
当然,从斯坦福拿任何一个学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有句话:“哈佛难进,麻省难出。”而斯坦福大学则是既难进又难出,它对学生一贯采用严进严出的做法。有人认为只要给斯坦福大学捐一大笔钱就能“混”进学校,这个想法完全错误。因为斯坦福大学并不缺钱,更不会为了钱砸自己的牌子(哈佛等大学同样杜绝这种达不到要求的学生入学)。根据斯坦福大学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其本科生的四年毕业率只有75%左右,即使到第六年,毕业率也只有95%。也就是说,有1/4的学生四年内完成不了本科学位,有5%的斯坦福本科生最后拿不到学位,淘汰率比中国最好的大学不知道要高多少。斯坦福大学博士生的淘汰率就更高了,很多人读了几年因为无法通过博士资格考试(Qualification Exam)不得不拿个硕士学位走人。以斯坦福大学电机工程系为例,每年大约有一半的学生要被资格考试刷掉,当然每个人有两次机会。
除了为硅谷提供技术支持和培养人才外,斯坦福大学在帮助硅谷转型方面贡献很大。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硅谷的支柱产业是半导体。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斯坦福大学孕育出的思科公司、太阳公司和SGI公司(即太阳公司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主要竞争者),推动了整个硅谷从半导体到硬件系统的转型。上个世纪90年代末,诞生于斯坦福大学的雅虎和Google,以及无数小的互联网公司掀起了互联网的热潮,实现了硅谷的又一次转型。今天,斯坦福大学在能源、材料等方面的一些新技术正在帮助建立太阳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产业,这个产业的规模可能比互联网更大,而它在医学研究上很多早期阶段的努力,比如在癌症治疗和抗衰老方面的研究,在更基础的生命机理方面的研究,也正在慢慢转换成可以实用目能改变人类生活的技术。一方面斯坦福大学带动了地域经济,另一方面它又是硅谷崛起最大的受益者。硅谷的公司为斯坦福大学提供了巨额的研究经费和捐赠。在历史上,惠普、思科、Google和太阳等公司都是斯坦福的赞助者。仅共同创办惠普公司的休利特家族(严格来说是休利特基金会)2001年就向斯坦福大学捐赠了4亿美元,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教育机构收到的最大一笔捐赠。2005年,斯坦福收到的捐赠首次超过了哈佛大学,完全是托Google创始人和员工的福。斯坦福受益于硅谷的地方远不止在财政方面。由于硅谷的发展,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就业率是全美国最高的,很多优秀学生正是冲着找工作方便这一点才选择斯坦福大学的。守着硅谷自然有得天独厚的创业和与工业界合作的机会,这又成为一些优秀教授选择斯坦福大学的原因。正是靠着硅谷的兴起,斯坦福大学才从二战后的一所地区性大学一跃成为美国一流大学,继而又成为全球顶尖的大学之一。
政府资助的研究课题不仅偏向于理论研究,而目也未必有很大的研究前景。大学教授看上去自由自在,可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不像公司员工被绑在上司安排的任务上,但是没有经费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大学教授天天围着经费转,政府有什么任务他们就不得不申请什么课题。几年前在欧洲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各国专家就这个领域今后的研究方向争论不休,贾里尼克教授听得不耐烦了,讲道:“你们在这里吵来吵去白浪费时间,还不是政府给你什么钱,你就做什么课题。”这是一个大家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但也道出了实情。在2000年后的一段时间里,计算机科学在美国进人低潮,很多计算机科学家都转行去搞生物统计和生物信息处理了。但是现在,大量学习生物统计的博士生毕业了,而学术和工业界对生物统计的需求并未增加多少,很多博士将在很长时间里找不到工作。这是政府计划很难避免的情况。
3 纽曼加洪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长曾经在毕业典礼上开过这么一个玩笑:“诸位,你们知道以前我们伯克利的毕业生是如何称呼斯坦福毕业生的吗?我的上司(My Boss)!”他的意思是在公司里当老板的常常是斯坦福的人,干活的是伯克利的人。接着他又说:“这种现象直到出了埃里克·施密特(Google前CEO)才终止。”当然,大家都知道施密特是个特例,而他前半句话说的却是普遍的现象。为什么斯坦福大学能培养出这么多优秀毕业生,尤其是工业界的领袖呢?这一方面是因为斯坦福大学守着硅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另一方面和它的教育方式有关。
斯坦福和美国东部的著名大学有很大的不同,这不仅体现在研究上,也体现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上。美国东部的名校比较传统,用中国唐代韩愈的话说,它们的任务就是传道、授业和解惑。它们对教授和学生要求都比较严,加上教授们专注于教学,因此教学水平非常高。比如在麻省理工学院,本科生的基础课微积分从来都是由最好的数学教授说授的,这一点在斯坦福大学就做不到。因此,很多学生和家长都知道在东部名校更能“学”到知识,而斯坦福大学更倾向于让教授和学生自由发展。它对教授和学生都是外松内紧,自由度大得多,对于有的学生来说可能是如鱼得水,对于没有动力的学生可能就荒废了时日。单从知识的传播来看,斯坦福大学还是赶不上东部名校。很多斯坦福大学的教授都承认这一点,甚至认为相比邻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有一定差距。
这种差异的形成有传统和地域上的诸多原因。美国东部的著名大学,以常青藤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大学为代表,沿袭并长期以来执行欧洲尤其是英国早期(不是现代)传统的“高等、教育”的原则。所谓高等,是指大学为社会培养高素质、有文化和有教养的(本科)人才,实际上是私人贵族教育的社会化。这些大学本质上不是职业教育的机构,而是培养绅士的地方。这与中国孔子时期的教育理念有不谋而合之处一一教育的目的不是传授实用技能和进行职业训练,而是教授礼仪、修养和德行。直到19世纪末,哈佛等大学的教育仍以拉丁文为主,有一点像中国古代强调“六艺”。到了19世纪,由于英国牛津运动的出现和德国洪堡体系的诞生,欧洲的大学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而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很多青年人不得不到欧洲求学。所幸,就在斯坦福大学诞生之际,欧洲这两项变革已经完成,大学教育的观念在美国开始改变。
说起现代高等教育,一定要提到两个人,普鲁士德国的外交家和教育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及英国的牧师和教育家约翰·纽曼(John Henry Newman)。
洪堡是普鲁士德国的外交家,却建立了完善的、服务于工业社会的普鲁士教育体系。德国有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学。在这个体系中,职业教育、技能教育成为大学的中心任务,这样大学生在学校学到的就是真正有用的知识,一走出校园就能马上为社会服务。洪堡体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研究对于大学的重要性,它将大学从一个教育机构变成了一个教育和研究的综合机构。在强权的普鲁士,一种体制很容易被自上而下地推广。普鲁士得益于洪堡的高等教育体系,很快从欧洲一个农业国实现了工业化,并目一跃成为19世纪欧洲最强国。德国的高等教育至今基本沿用200多年前洪堡制定的体制,保证了它在全世界工业界和商业界的领先地位。洪堡体系后来对美国、俄国和中国等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马上搞了将理工专业分离的院校调整,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原来的综合性大学拆成文理型大学、工科大学、政法学院和医学院等,完全是按照洪堡的体制来的。遗憾的是又没有学到家,“忘了”在大学里建立研究生院,以至于研究生教育至今落后。
美国著名教育家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Gilman)等人借鉴了洪堡体系的长处,将美国的很多大学从近代的私塾转变成高等职业教育和研究的机构。吉尔曼生长在美国东部,却在美国西海岸担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短时间的校长。在加州的短暂时光让吉尔曼看到了大学开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由于加州政府试图把伯克利办成一所农业大学,吉尔曼的理想遂难以实现。这时正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刚成立,并聘请他来担任第一任校长,吉尔曼实现自己理想的舞台便顺顺当当地出现了。吉尔曼不负众望,按照德国职业教育的模式,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起美国第一所研究生院,并把该校办成了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在长达25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生涯中,吉尔曼不仅把该校办成了一流的大学,而且在美国普及了研究型大学的概念。几年后,他的同学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也把康奈尔大学从一所小小的乡村学院办成了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后来,吉尔曼又担任了卡内基学院的校长,奠定了今天卡内基–梅隆大学在工科界一流的地位。
斯坦福大学诞生的契机很好,当时正是美国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转型的时期。利兰·斯坦福为了给斯坦福大学找一位好的校长,遍访美国东部名校。他在康奈尔大学见到了校长安德鲁·怀特,怀特曾经随吉尔曼一同到欧洲考察高等教育,他办学的原则和吉尔曼很相近。作为铁路大王和政治家出身的老斯坦福,非常认可吉尔曼和怀特的办学理念,因此两人谈得非常投机,于是斯坦福希望怀特能接受斯坦福大学校长一职。怀特因故不能接受邀请,但向斯坦福推荐了自己年轻的学生、印第安纳大学的校长戴维·乔丹,即后来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乔丹领导下的斯坦福大学,从一开始就避免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走过的弯路,直接成了研究型大学。
斯坦福大学一直有重视研究、重视博士生教育的传统。这不仅仅表现在科学和工程学上,而且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也是如此。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是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和政策研究中心,曾任美国国务卿的赖斯原来就是那里的学者。斯坦福大学在上个世纪初成立了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后来从斯坦福大学分离出去,即现在的SRIInternational,是美国著名的信息科技和国防科技研究中心。
凡事有利必有弊,教授的时间是有限的,搞研究或者办公司的时间多了,在本科生教学上投人的时间自然就少了。这就是斯坦福大学本科教学水平赶不上普林斯顿大学,甚至比不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原因。但是即便如此,我个人仍然认为一个本科生在斯坦福比他在普林斯顿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能学到更多的东西。这里面就涉及对大学办学理念的理解了。
我不是大学教育研究的专家,我的看法可能有些片面之处。对于大学的理念,我个人非常赞同英国牛津的主教、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的发起人约翰·纽曼的观点。纽曼有点像围棋里的求道派,在他看来,大学是传播“大行之道”(Universal Knowledge)而不是雕虫小技的地方。纽曼在他的著名演讲“大学的理念”(Ideas of University)中说道:
“先生们,如果让我必须在那种由老师管着、修足学分就能毕业的大学和那种没有教授和考试,让年轻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互相学习三四年的大学中选择一种,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为什么呢?我是这样想的:当许多聪明、求知欲强、富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锐的年轻人聚到一起时,即使没有人教,他们也能互相学习。他们互相交流,了解到新的思想和看法,看到新鲜事物并且掌握独到的行为判断力。”
今天,包括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内的英国一些大学依然遵循纽曼的这种理念。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每个学院(College),比如剑桥大学著名的三一学院(出过著名科学家牛顿)和国王学院,其实都是由不同学科的学生和单身教授吃住在一起的生活小区,而不是我们常说的工学院、文学院等专业学院。目的是为了让大学生们在生活中䶼相学习。在美国,很多研究型大学在强调职业培训的同时,依然遵循这个大学的理念。以职业教育而著名的哈佛商学院(HBS)其实把纽曼的这一理念发展到了极致。在这所全球最难进的商学院里,从来没有考试。同学们䶼相学习获得的知识不比从教授那里得到的少。大家生活在一起,平时同吃同住,放假由学校组织到世界各地一起玩,那里的学生大多都是已经小有成就而又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们在宽松的环境下,可以自由地获取专业技能和社会知识,尤其是和人打交道的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哈佛商学院里不能和同学们玩到一起,就白交学费了。斯坦福大学在这方面当然没有哈佛商学院那么夸张,但是它给了本科生一个类似的内紧外松、自由发展的环境。
纽曼的教育方法要求受教育者有很高的自觉性。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一所大学大部分学生都是问题学生,而学校又不加管束,这所大学一定办得一团糟。因此很多州立大学,生源参差不齐,很难实施纽曼的这个理念。和哈佛商学院一样,斯坦福大学的入学门槛很高,每年的招生人数只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1/5,来到这里的学生都是希望自己今后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学习的主动性是不用担心的。斯坦福大学的大部分本科生学习能力很强,能很快掌握专业知识,这样就有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立足于社会的基本知识和本领,也就是纽曼所说的“大行之道”(Universal Knowledge)。
纽曼教育理念成功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大学学生和文化的多样性。一所大学要想让学生掌握大行之道,必须让他们有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学习,也必须让他们互相之间有取长补短的可能性。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体会,学习计算机的同学聚在一起常常谈论一些和计算机或科技有关的话题,学习金融的在一起常常谈论对经济的看法。如果一所大学都是由同一类年轻人构成,他们取长补短的结果不过是补充了专业知识,而不是大行之道。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等优秀大学易然在工程上不比斯坦福大学差,但是无论是专业、课程和生源都太单一。进人麻省理工学院的高中毕业生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学习理工。这些年轻人在一起不断交流,彼此在技术上越来越精深,内境愈宽,外延愈窄。在互联网刚兴起时,我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博士生谈论过各种浏览器的好坏,他们不和你谈微软的IE或Mozilla的火狐,而是谈UNIX用户更常用的字处理器Emacs下一个浏览网页的小众功能,这个东西不仅不好用,而且在全世界用它的网民连万分之一都不到。他们和你谈的是技术上谁实现得好。这些人以后可能是很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但很难成为创业者。2016年AlphaGo战胜李世石之后,人工智能在美国大学里很热门,我接触到的斯坦福的学生大多想利用人工智能赶快做点什么事情,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则在挑AlphaGo相比人的不足之处——耗电量太高,训练量太大。这些本身并没有错,做学术研究是很好的课题,但是对于创业者来说,需要的是尽快倬用成功的技术,而不是给它们挑刺。
斯坦福大学则不同,它的学生来源非常多样化、多元化,从文理、工程、医科、商业到法律什么都有。很多人到了斯坦福并不把自己限定在一个专业上。可以想象,一个计算机博士在和一个住院医生谈论浏览器时,就必须用最通俗的语言进行交流,而不是对各种技术评头论足。同时,他可以了解到一位医生对浏览器的需求,比如易用性、安全性,等等。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来自于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易然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中一半是外国人,但是很多大学的本科生都是美国人、本州人,甚至本地人。不难想象从小在同一个地区长大的孩子说来说去就那么点儿话题,不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就无法想象天地之大、世界之多样。
斯坦福大学的很多学生不仅在学业上出类拔萃,而且有各种各样的特长。我的一位朋友在高盛做投资,是非常成功的投资人,他也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年轻时还是ATP职业网球选手,一度排在世界二十几名。比如在体育方面,斯坦福大学出了很多奥运会冠军和世界冠军。斯坦福大学的游泳队曾经是半支美国奥运游泳队,出过获得四枚奥运会金牌的埃文斯等一大批泳坛名将。从1912年起,斯坦福大学在历届奥运会上至少获得一枚金牌,最多的一次多达17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获得25枚奖牌,其中8枚金牌。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排在法国之前,列第十位。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斯坦福的成绩进到了第八名,共获得12枚金牌,在2016年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他们的成绩进步到第六名,再获14枚金牌(其中一枚是代表希腊出战获得的)。斯坦福大学还出过网球巨星约翰·麦肯罗和高尔夫球巨星老虎伍兹。斯坦福大学的橄榄球队和篮球队都是美国一流的。这些运动员并非只是靠体育成绩受照顾进的斯坦福大学,他们大都在学业上同样优秀。这些奥运会冠军就和大家住在同一栋楼里,一起上课。
斯坦福大学没有音乐学院,只有一个不大的音乐系,著名钢琴家斯坦恩(Issac Stern)(生前)和大提琴家马友友却经常到斯坦福演出。斯坦福大学有全世界最多的罗丹雕塑收藏,包括他最著名的作品《思想者》。(罗丹的每一件雕塑作品一般都有不止一件但不到十件真品,原始的模具在这几个真品浇注完毕后毁掉。他的《思想者》在法国和美国有几件真品,相䶼之间没有区别。)此外,斯坦福还收藏了从东晋到明清的瓷器。对年轻的学生最有益的校园环境,就是那种最贴近今后真实生活的社会环境。在斯坦福大学,人员的构成和真正的社会并无太大差异,每一个年轻人周围又是各个行业的佼佼者,在这种环境中互相学习几年,外延就变得宽阔起来。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讲,在斯坦福大学的岁月里学到的社会知识比课堂知识对自己的一生更有帮助。拉里·佩奇在Google成功后回到斯坦福大学介绍他成功的经验时强调的一点是,创业者要成为全才(他的原话是:Be an expert in all aspects.)。从培养全才的角度来看,斯坦福大学无出其右。
其他大学有心学习斯坦福大学的经验,却难成功。目不说众多州立大学因为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很难和斯坦福大学相比,就是其他名牌私立学校由于种种原因,也很难像斯坦福大学那样兼得纽曼教育和洪堡教育之长处。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太单一,学生过早地开始了职业训练,多多少少便有了“呆气”。即倬是哈佛和耶鲁等综合性大学也很难创造斯坦福大学的奇迹,由于历史原因它们在工科职业教育上非常弱。哈佛大学一直想弥补工科方面不足的缺陷,利用自身的名气聘请了很多著名教授,但是仍然只建立起一个象牙塔式的小规模、没有什么影响的工程院。它一度试图合并麻省理工学院,但是没有成功,因为后者不愿意。
4 硅谷孵化器
硅谷为斯坦福人提供了经费和实实在在的课题,让学生们容易找到合适的创业题目,加上宽松的环境为教授和学生的创业行动大开绿灯,良好的教育使得很年轻的学生也可以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东风就是学校最后扶持一把。我看过一则关于肯尼迪总统和美国导弹之父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钱学森的导师)的故事。1963年,冯·卡门被授予美国第一个国家科学奖,这是在美国人心目中比诺贝尔奖更高的荣誉,每次由美国总统授予。当冯·卡门在肯尼迪总统的陪同下走下白宫的楼梯时,这位81岁高龄的科学家一个趔趄差点摔倒,肯尼迪总统立刻上前搀扶。这时,冯·卡门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年轻人,当一个人往下走的时候是不需要扶的,当他往上走时恰恰需要你扶他一把。”
在扶持学生创业方面,斯坦福大学无疑做得非常好。它对创业的教授和学生直接的帮助就是在他们和工业界之间搭建桥梁。斯坦福大学有一个办公室,专门帮助想创业的在校学生与在硅谷成功的校友,或者和斯坦福大学有来往的企业家、投资家建立联系,寻找投资。
Google的佩奇和布林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找到第一笔投资的。1998年,在开发Google搜索引擎没多久,这两个创始人很快就用光了手头不多的现金和信用卡能透支的全部额度。他们自己也曾努力寻找过天使投资,但当时只是两名普普通通的博士生,在硅谷多如牛毛的创业者中并不引人注意,所以开始找钱并不顺利。这时他们通过学校这个帮助学生创业的办公室,联系上了太阳公司的创始人安迪·贝托谢姆。贝托谢姆易然是计算机技术出身,但是对搜索引擎技术并不熟悉,之前也没有用过Google的搜索。因为是母校介绍的,贝托谢姆还是在百忙中约见了这两个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据佩奇讲,贝托谢姆很忙,跟他们约在上班前于公司见面,他和布林带着服务器到了安迪的办公室,贝托谢姆当场搜索了一些东西,非常满意,当即开出了十万美元的支票给了他们。这就是Google作为一家公司的开始。易然这笔钱没多久就用完了,但是这笔钱的广告效应远远不止这十万美元。之后有些投资者听说太阳公司的创始人、工业界的领袖给Google投资了,也就相信了Google的水平。在Google最早的投资人中,包括篮球明星奥尼尔、身为电影明星和后来的加州州长的施瓦辛格等根本不懂技术的天使投资人。这些人是通过一个天使投资团,跟着贝托谢姆糊里糊涂地发了一笔财。
可以想象,如果佩奇和布林不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他们很难有机会直接向一位工业界领袖推销自己的发明。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在中国清华或北京大学的一位普通研究生有没有可能通过学校直接见到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斯坦福大学能做到这件事,正是它了不起的地方。
易然所有大学基本上都设有联系校友的机构,可是很多都形同虚设。但是美国很多著名大学,包括斯坦福大学的这种机构是实实在在地经常和校友,尤其是事业有成的校友联系。它们会有专人定期拜访各地杰出校友并通报学校的情况,既分享学校的发展成就,也通报学校遇到的困难。遇到后一种情况,很多有钱的校友会倾囊相助,而斯坦福大学对慷慨的捐赠者给予衷心的感激和很高的敬意。在斯坦福大学,可以看到很多由校友捐助的大楼,比如帕卡特(惠普创始人)楼、杨致远楼,等等。正是由于联系紧密,校友们才会在离开学校后不断帮学校的忙,帮着师弟师妹们创业。
斯坦福大学有一个非常闻名的风险投资论坛一一斯坦福企业家之角(Stanford Entrepreneurship Corner)。光看名字有点像中国的英语角,但实际上它是由工业界和著名大学教授轮流主说的论坛。经常来这里的人包括很多著名的风险投资家,比如KPCB的约翰·杜尔;工业界的领袖,比如Google前CEO施密特和创始人佩奇、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以及哈佛商学院和斯坦福商学院的许多著名教授。这样,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就有机会接触到世界级的投资人和工业界领袖,从而有机会找到投资渠道,更可以从著名投资人和工业界领袖那里得到创业上的指导,大幅提升创业的境界。
美国每所大学都或多或少有些毕业生能成功创办各种小公司,但是能将小公司办成主导一个行业的跨国公司的则是凤毛麟角。而在信息产业的主导公司中,由斯坦福大学校友创办的公司可能占到一小半。妨碍一个创业者成为业界领袖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两条值得特别注意。第一是好高骛远。关于这一条在前面已经多次提及,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第二就是小富即安。很多人办公司都本着捞一把的想法,而不是做一番事业,这些人归根结底是创业的境界不够高。而这种境界是不可能从课堂上学到的,只有经常和世界级的人物在一起切磋,一个人的境界才能有质的提高,他才能站在巨人的肩上。在世界上至今找不到第二所大学能够像斯坦福大学那样让普通学生有机会不断接触到工业界和商业界的领袖。
斯坦福大学鼓励创业的另一项具体措施是对利用职务发明创业的宽容。之前介绍思科公司时提到,思科创始人的发明完全是与工作相关的职务发明,而在很多大学和实验室,专利的所有者即雇主严禁个人利用职务发明来创办公司。斯坦福大学在这方面相对比较开明,只要大家坦诚地协商好将来利益的分配,它甚至鼓励学生和教授利用职务之便创业,但斯坦福大学要的股权一般都少得可怜。我们前面提到的亨尼西创办的MIPS公司,包括Google公司都用了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而斯坦福只占了一点股份就如同低税率可以刺激经济一样,从长远来讲斯坦福这种少占股份的做法是双赢的,一方面可以鼓励创业,另一方面,作为对母校的感激,几乎所有创业成功的人都非常慷慨地给予了斯坦福大学巨额的捐助。
为了方便外国学生创业,斯坦福大学甚至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设法维持他们在美国的合法身份。根据美国移民法律,外国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将不再拥有学生身份(F1签证)。如果不能获得工作签证(H1),那么这些学生最多只能以实习的身份(Practical Training)在美国再待上一年。而获得工作签证的前提是被一个雇主(比如公司或者大学)以足够高的薪水雇佣。这样外国学生一毕业直接创业就会面临身份问题,而身份问题不解决,投资人也不敢投资。对此,美国大部分大学的态度是,“你毕了业,我就管不了你了,身份问题自己去解决。”而斯坦福大学则可以通过延长毕业时间帮助外国学生维持合法的身份,当然这是打移民法的擦边球。据斯坦福大学校友,在美国和中国成功创办多家公司的金学诚博士介绍,他在斯坦福完成博士论文后想自己创业,但是苦于一旦毕业就没有了合法身份,于是找学校求助。学校同意他推迟递交论文的时间,斯坦福大学告诉他,在他提交论文之前,他每学期只要修一学分的课程即可。由于为了创业没有时间上课,学校建议他修一门高尔夫球的体育课,权且算是锻炼,不会成为额外负担,于是他打了四年高尔夫球。金博士有一次在向中国政府官员介绍硅谷成功经验时提到:“正因如此,斯坦福校友事业有成后,都不好意思不给学校捐点钱。”学校帮助自己学生成功,然后学生再回报母校,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除了为创业者提供便利的创业条件,斯坦福大学对创业者第二大的帮助就是营造了创业的气氛和传统。很多大学都试图效仿斯坦福大学鼓励学生创业,然后从成功的创业中获得长期回报,但是在整体上却没有营造出创业的气氛。麻省理工学院一直以培养工业界领袖为己任,并且成功地培养了大量的工业界主管,但是自己办公司的学生远不如斯坦福大学的多。不少风险投资家也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校园里转悠,希望能找到好的项目投资,但是效果一般。加州理工学院有一系列专门培养工业界领袖的必修课程,但是大部分毕业生反而进了学术界。这些名牌大学缺乏创业的氛围。哈佛商学院要求每个人都要提出和制订创业计划,并目给予前几名的学生创业经费,易也扶植出了一些小公司,但是它们都没有成为一个行业的领头羊,更没有开创新的行业。所以,这么多年来不论是像麻省理工学院这样著名的工科大学,还是像哈佛商学院等著名的商学院,都没能重现斯坦福大学的奇迹。
创业的氛围非常重要。在一所有创业氛围的大学里,创业是一种主动自发的行为,创业者出于对一项技术及其商业应用的极大兴趣,将它的实现作为自己的理想,这种动力对于创业的成功不可或缺。反之,如果光靠别人来推动创业,是鲜有成功的。只有主动的创业,创业者才能从亲身实践中找到好的创业题目,并为之奋斗。反之,即使有了好的题目,也会半途而废。我参加过某所著名工科大学在硅谷为风险投资家举行的项目介绍会,该校为了鼓励学生创业,规定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必须完成一项发明和设计才能毕业,在介绍会上他们拿出了一些很好、很有新意的发明。但是这些发明大多数是学生们作为完成教授任务或拿学位的要求而做的,根本就没有想过将这些发明产品化而挣钱。因此,他们在选题时很多题目易然好却只能将技术卖掉,根本无法开办公司。即倬有一些好的选题,因为和自己今后的事业无关,学生们也根本没有仔细考虑商业化的许多繁杂的具体问题,因此面对风险投资家的提问茫然无所知。由于缺乏创业的热情,几乎所有的学生一旦完成学位的要求离开了学校,所做的工作就半途而废了。第二年,新的学生重复学长们做的无用功。当然,这种训练对学生的能力有很大提高,但是对创业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人们想象中,商学院的学生就应该热衷于创业,其实不然。虽然很多商学院为学生营造了各种创业条件,但是他们创业成功的案例还不如学习工程的学生多。我参加过风险投资对一所著名商学院的一些学生创业项目的评估。也许是学习商业的原因,他们提出的题目都很大,但是很多要么是夸张,要么是没有实际内容。其中一个项目类似于网上建立一个社区,自己设计贺卡、T恤衫、纪念品和邮票并且通过社区进行交流。这家公司的盈利模式就是从相互有偿的授权(License)中分得一块利润。这个题目不能说没有用,而且提出者也一定做了不少研究。但是,这里面我看不到任何的技术和商业特点能够阻止别人进入该领域竞争,更何况其市场规模比他们估算的小很多。第二个项目很有代表性,项目本身大得难以置信,叫做互联网3.0。问及是否清楚互联网2.0的定义,他们不置可否。又问他们这互联网3.0能带给用户什么好处,他们也不置可否。最后问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他们认为,第一,在当前的互联网领域,雅虎和Google等公司已经处在主导地位,很难撼动,只有提出一种超前的概念才能打败这些公司。第二,这个题目足够大,风险投资也许会有兴趣。我们再问他们此前做了多少研究,发现他们确确实实做了很多研究,看了很多参考资料,图书馆里的、互联网上的,但是他们的项目无异于闭门造车。第三个有代表性的项目就是把各种美国已有技术和商业模式搬到中国和印度去,提出者以中国和印度学生居多。比如前几年有人把eBay搬到中国搞了易趣很成功,他们提出把YouTube搬到中国和印度去(当时中国还没有那么多的视频网站)。这些项目有些后来还真得到了资助,但是这种模仿和改造的项目最终并没有成功,因为你能模仿,别人也能模仿,没有什么门槛。最有意思的是一个中东来的学生想来想去还是倒卖石油来钱最快,连他的同学也笑了,说除了你,我们可没有这种机会。读者可能已经看出这里面的问题,这些都是学生们为了完成学业,挖空心思想出来的项目,与太阳的工作站、思科的路由器、雅虎的网站和Google的搜索引擎这些源于创业者科研实践的项目完全不同。
环境是可以影响人的。在斯坦福大学这样创业成风的环境中,一个计算机系或者电子工程系的博士生不想自己创业有时可能都会不好意思,而创业失败也没有什么可自卑的。佩奇原来所在的计算机系数据库实验室,前前后后出了无数开公司的学生,以后的博士生一进去就耳濡目染办公司的事情。而在绝大多数大学里,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并不是这样,导师希望学生只专注学术,而博士生则是以进人学术界为荣。比如我以前所在的约翰·霍普金斯语言和语音处理中心(CLSP),在我之前所有的博士生毕业后全部去了大学和大公司的实验室(比如IBM、AT&T和微软的实验室),没有真正到工业界工作的,更不用讲创办公司了。当时我到Google工作,在所有师兄弟中纯属异类。但是,自从我到了Google,后来的人发现这条路也很不错,以后所有的博士毕业生都会来Google面试,每年都有人来Google,就连以前在大学和大公司实验室的师兄们也有跳槽过来的,这就是风气的作用。另一方面,人也会选择环境。很多学生挑学校时也是看中了斯坦福大学守着硅谷将来能创业这一点。
虽然不是每一个斯坦福人都能创业,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领导者,但是他们中间很多人可以成为很好的合作者和追随者。佩奇有一次在斯坦福大学的创业论坛上讲,创业的关键之一是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在斯坦福大学找到一起创业的追随者相对容易。首先,进人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大多愿意到刚成立的小公司工作,而很多东部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并不愿意。其次,由于斯坦福大学的这种内紧外松的环境,学生们交际的圈子相对较广,容易打造一个可以互补的创业团队(Founding team)。而在完全追求学分的大学里,每个人能深入了解的大多是自己的同班同学,或者同实验室的同事,但朋友之间的互补性不强。
世界各地每时每刻都会诞生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但是将它们最终变成产品,变成一个新的行业需要一个像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孵化器。韩愈讲,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于是便见不到千里马。同样,发明创造世界各国都有,而斯坦福大学只有一个,因此,硅谷的奇迹就难得一见了。
结束语
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学硅谷的经验,办起了自己的科技园。尽管有些地区自称是“××的硅谷”,并目带动了地区性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但是并没有孕育出像思科、雅虎和Google这样具有开创性的世界级公司。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缺乏一个像斯坦福大学这样的新公司乃至新产业的孵化器。关于斯坦福大学更多的介绍,读者朋友可以阅读拙作《大学之路》。
斯坦福大学大事记
1885 斯坦福大学成立。
1893 老利兰·斯坦福去世,斯坦福大学资金被冻结。
1899 斯坦福夫人简·斯坦福经过六年的努力终于使得资金解冻,斯坦福大学度过早期财政危机。
1929 斯坦福大学毕业生胡佛成为美国总统,由于在他任期内美国(和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他被认为是美国最差的总统之一。
1951 特曼提出通过出租土地集资办学的办法,硅谷诞生。
1952 斯坦福大学获得第一个诺贝尔奖,到2018年,斯坦福的教授一共获得了31个诺贝尔奖。
1965 计算机系成立,此后该系毕业生在硅谷创立了很多成功的公司。
1970 斯坦福成立了技术授权办公室(OTL),推进技术转让和实用化过程,并帮助教授和学生创办公司。
1973 斯坦福完全取消了在招生上有关男女比例的限制。
2012 斯坦福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一个教育和研究中心。不过2017年斯坦福暂停了与北京大学合作的“海外本科学习计划”。
第18章 挑战者 Google公司
长期以来,硅谷的公司在和微软的竞争中一直处于下风。不但在市场上被微软挤垮,在人才的竞争中处于下风,而目在官司上也打不赢。从苹果、太阳、Novell到网景公司,一个个被微软后来居上,两三个回合就被打败,从此没有能够全方位成功挑战微软的公司了。号称世界创新之都、有几十万IT从业人员的硅谷一直梦想着有一家公司能够在和微软的正面竞争中赢一次。这个梦想终于由一个历史很短却有着惊人发展潜力的婴儿巨人(Baby Giant)Google公司实现了。
Google公司从一开始就以一个挑战者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它不仅在技术和商业上挑战比自己更大更强的公司,而且在理念上挑战传统。到2018年底它(的母公司Alphabet)已经是一个员工数量超过10万的跨国公司了,而且还在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创造奇迹。Google的故事完全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已经有人写了,以后还会有人再写。遗憾的是,大多数书无非是对一个成功者的吹嘘和对Google所谓奢侈生活的描述,很少提及Google成功的真正原因。对于公众都熟知的事实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在这一章里,我想用16个瞬间,也是16个不为人知或被公众忽视的侧面,来描述一下这个传奇的公司。通过这些侧面应该很容易了解Google成功的原因。当然,我所描述的Google是2016年之前那家充满活力的公司,而非今天比较平庸的这家大公司。在我看来,2016年之后的Google,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多。
1 最轰动的IPO
……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和投资者的利益,并目保证公司在上市后不受华尔街控制(我们在前一章介绍过华尔街是如何控制上市公司的),Google在IPO时做了三件惊人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采用拍卖的方式决定IPO的股价。为了回报广大股民对Google的支持,并保证中小投资者的利益,Google最终说服了华尔街投资银行采用竞标的方式认购Google的原始股。在以往的上市行动中,原始股的价格由要上市的公司和承销商谈判商定,一般来讲,价钱都低于实际价值(只有黑石公司上市时除外),而承销商和它们的大客户则赚差价,这样当然就损害了要上市公司的利益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比如,百度公司上市时的定价只有区区27美元,是上市第一天收盘价的1/4。不仅如此,承销商还会控制原始股的配给,除非是它非常重要的大客户,一般人根本拿不到什么认购权,这样就无法保证中小投资者的利益。Google的做法保证了自己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当然华尔街就要少挣一点。这一点,后者也心知肚明,明面上不好讲,背地里并没有配合Google。因此,居然出现了Google首次募资原始股认购不满的情况。Google公司当机立断,在上市的前一天调低了一些原始股价格,同时大幅降低了融资的金额,从原来的27亿美元降到17亿美元,避免了以过低的价钱大量稀释自己的股份。
Google上市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将一次融资拆成三次。一个公司融资上市,当然希望融资越多越好,但是这样要大量稀释自己的股票,公司和现有的股东未必能得到最大利润。显然Google第一次没有充分融资。在首次融资一年后的2005年9月,Google进行了第二轮融资,以295美元的价格再次融资42亿美元。这次融资易然金额大,但是由于Google的股价比IPO时涨了三倍,只增发了很少的股票,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自己和投资人的利益。到这时,大家不得不佩服Google的高明。Google的上市融资行动至此仍然没有结束。当时大家都奇怪著名的高盛公司没有参与第二轮融资,而自从Google上市,高盛一直是在为Google高调捧场的。半年后,谜底揭晓了。2006年5月,美国的标准普尔指数将Google纳人其中。从金额上讲,标准普尔500指数是美国和世界上的基金中,作为参考依据最多的指数,Google被纳人其中后,很多基金将自动按照标准普尔500指数指示的比例购人Google的股票。根据以往其他股票被列入该指数的历史表现,股价会上涨10%一20%左右。通常炒家们在得到这个消息后会打个时间差从中套利(在对冲基金中专门有一种投机这种交易的基金,称为事件驱动基金)。Google则早已计划并目准备好了,利用这次有利时机进行第三轮融资。因此,标准普尔宣布这一消息后,Google马上宣布第三轮融资20亿美元,这次由高盛公司独家承销。Google在两年多时间里,三轮融资共80亿美元,而目只稀释了不到10%的股份,成为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上市行动。有了这些现金,Google就有足够的财力打造超级数据中心,在与微软和雅虎的竞争中占到有利地位。和巴菲特一样,Google的前任CEO施密特是一个非常“爱财”的管理者,他永远将现金储备作为他关心的头等大事。在2008年他接受了媒体记者的一次采访。当记者问到Google有上百亿美元的现金,能否给股东发一点红利时,施密特开玩笑说,我更喜欢看着这些钱在公司的银行账户上。和很多成功的职业经理人一样,施密特是一个非常稳健的管理者,他在做任何事时都会保证在最坏情况下Google能挺过多道难关。
Google上市时做的第三件非同寻常的事就是学习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将Google的股票分成了投票权完全不同的两种。佩奇、布林和施密特等人追求长期利益而不是只顾眼前利益,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巴菲特非常一致。当然,华尔街对于任何上市公司都会指手画脚,要求它们达到每个季度的营收预期。当基金经理们在一个上市公司中占的发言权很大时,他们甚至会要求撤换整个董事会由他们直接管理。2008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卡尔·伊坎威胁撤换雅虎董事会一事,就是投资人过度干涉上市公司经营的典型例子。正是因为这个原因,Google迟迟不愿意上市。Google的创始人仔细研究过巴菲特的成功经验,发现其中成功的一条就是公司内部的人要有绝对的发言权(投票权)。巴菲特的做法是发行A和B两种面值不同的股票,A股的面值是B股的30倍,投票权却是B股的200倍。B股永远不能转成A股,但是反过来A股可以在任何时间转成B股。当然,巴菲特和芒格等其他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大股东及大投资人拥有的是A股。由于A股的股价每股高达十几万美元,不仅散户无法购买,动态管理的基金经理也无法购买。这样就保证了巴菲特和芒格对公司的绝对控制。Google也做了类似规定:2002年以前发行的股票(B股)每股拥有10个投票权,而以后的称为A股(包括所有公开交易的),一股只给一个投票权。B股(大多数掌握在创始人和高管手里)不能流通,只有换成A股才能出售,而A股则永远不能转换回B股。其结果是不管一个投资人从市场上购买多少Google的股票,只要Google创始人持有10%的股票就可以拥有绝对多数的投票权。这样,华尔街就很难直接干涉Google的发展。后来,百度和京东也从Google身上借鉴了双层股权结构的做法。
从Google的上市过程中可以看到,这家公司眼光长远,且精明到了骨子里。
2 早期岁月
3 商业模式
……
佩奇是一位极具商业眼光,并目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奇才。在Google刚成立不久,公司请了美国第二大卫星电视网EchoStar(Dish Network卫视的提供商)的老板来公司做报告(Google经常请一些各行各业的精英,甚至包括太极拳高手,来公司做报告,不管他们做的事是否和Google有关)。当时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互联网公司基本上死光了,其他的公司都在萎缩,而EchoStar的事业居然蒸蒸日上。当时EchoStar市值是一百多亿美元,比(缩水后的)雅虎可大得多。听完EchoStar的报告,佩奇下来讲,你们看到了吗?EchoStar的东西其实都不是自己的:它不会做卫星,因为它们是买来的或租来的;它自己不制作电视节目,而是从媒体公司授权获得的;它也不做卫星接收器(圆形的锅)和电视机顶盒,前者是从中国买的,后者是从摩托罗拉定制的。它做的事就是把电视节目送到终端用户家里。但是,就是这么一条,它就值上百亿美元。我不知道EchoStar的想法和佩奇是不谋而合,还是佩奇从EchoStar那里受到了启发。佩奇知道,只要把互联网的内容送到千家万户就行了,至于互联网的内容是谁的并不重要。世界上有上千万的网站(不包括垃圾网站)和上百亿的网页,绝大多数网站对于网民来讲很难找到,因此它们欢迎Google这样的搜索引擎来索引自己的网页,这样它们和搜索引擎才能做到双赢。今天Google的服务已经超越互联网索引的内容,但是Google所有的服务至今仍遵循这个原则,这是Google商业模式的核心。比如,Google新闻实际上不是它自己的,而是它索引别人的新闻,方便大家查询。Google最神奇的Google Earth也是从第三方手里买来的数据,Google做了一个易用的软件而已。
Google服务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直接面对最终用户,在这一点上佩奇和布林的想法和投资大师巴菲特不谋而合。巴菲特有一个最简单有效的选择股票的办法,就是到大小百货店、加油站和食品店看一看老百姓都在买什么,这比听华尔街分析师瞎掰似乎要准确得多。巴菲特因此而选择了可口可乐、宝洁、强生、百威啤酒、沃尔玛和卡夫食品等公司投资,都获得了极高的回报。在巴菲特看来,广大消费者才是一切商业的衣食父母。佩奇和布林也深深体会到,广大最终用户(网民和广告主)才是为Google带来生意的人,因此,Google的产品一直是针对广大用户并满足他们最基本的需求,既不像IBM那样针对企业,也不像苹果那样针对精英。这样的商业策略,好处是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不论经济形势好与坏,大家都要上网,就如同要购买日用消费品一样,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Google的商业风险。这就是Google前CEO施密特说Google有很好的能力抵抗经济衰退的原因。
在大的经营方向确定下来后,Google需要找到具体挣钱的商业模式。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后,搜索广告渐渐进人了佩奇的视野。在Google以前,Overture已经开始尝试按网站付费多寡对搜索结果进行排名,并目获得了相当的成功。Google一直强调网页排名的公正性,直接采用Overture的做法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影响Google的声誉,于是大家找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网页排名本身完全保持客观性,而在网页的其他地方嵌人付费广告。这就是Google AdWords的由来。对Google AdWords贡献最大的两个人是佩奇和当时的产品经理萨拉·卡曼杰(Salar Kamanger)。佩奇亲自领导了AdWords的开发工作,而萨拉具体主管了这个产品的开发。萨拉在当时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克服了很多困难,硬着头皮把这件事情做成了。在 AdWords的开发过程中,Google的团队展现出惊人的执行力,一共十几个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整个AdWords系统搞得停停当当,这件事情雅虎和微软花了十几倍的人力、几倍的时间也没有搞好。在Google的早期,公司里总是有一种豪情,相信自己一个人能当十个人倬,并目屡屡证明确实如此。
Google在商业上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将中间环节减至最少。Google认为,中间环节除了截留利润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因此,Google在中国以外的全球市场,向来只做直销,没有什么广告代理商。这一点,与戴尔电脑和GEICO保险公司的直销模型非常相似。在Google之后,苹果也取消了大部分的代理商,改由门市店和网站直销为主。
Google在早期并没有刻意追求营业额和利润,而是想方设法扩大用户群。除了在技术上要比对手做得好以外,还将自己的网页做得特别干净,这样在到处是铺天盖地的横幅广告和弹出式广告的互联网上,显得非常超凡脱俗,便吸引了很多用户。当用户规模很大时,在Google上随便放点什么广告,都会有很好的效果,因此,广告主都爱来Google。Google虽然广告投放数量不多,但是收费却比传统的互联网广告贵10倍。这才保证了Google的高收人、高增长。
4 个人英雄主义和群众路线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这个被争论了2000年的话题到了19世纪终于有了结论。现在,我们拿这个问题随便问一位受过良好中学教育的人,他都会按照老师教的说法回答是奴隶(或是人民群众),而不是英雄创造历史。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潜意识里并不这么认为。近二十年来,媒体时常公布中国上市公司收人最高的CEO名单。每当大众对一些老总每年拿过半亿的收人议论纷纷时,这些总裁总是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认为要不是因为他有三头六臂,哪有这公司的今天。在美国也是如此,雅虎前CEO塞缪尔尽管把公司搞得一团糟,却每年毫不脸红地拿上亿美元的收人。
中国上个世纪60年代鼓励“螺丝钉精神”,中心思想是每一个人的贡献是有限的,因此大家要绝对服从组织,对岗位不挑剔,踏实工作,默默奉献。它曾经影响了几代人,但是这种观点在强调个人价值的今天却不大管用了。然而这种个人服从大局的组织原则却又是任何一个集体取胜的关键,于是今天被冠予了一个好听的名称一—“团队精神”。
Google一直宣传团队精神,但是Google从不虚伪,并不要求个人无条件服从团队,因此在Google内部换来换去很常见。而早期的Google则更赞赏个人英雄主义,而目往往发扬个人英雄主义。
早期Google一共没有几个人,到1999年拿了凯鹏华盈和红杉资本几千万投资时,也不过区区一二十位工程师,所以Google强调的一直是以一当百。如果一个求职者不能做到这一点,Google就不会要。在软件开发上,早期的Google不相信软件工程里提出的什么将一个大任务细化后让初级程序员也能写程序这种普遍认同的观念。Google相信的是一个头等软件工程师能干10个二等工程师的活,一个二等工程师能干10个三等工程师的活。如果是三等工程师,Google根本就不要。除了前面提到的西尔弗斯坦,早期Google的员工个个都是人物。比如来自中国、在美国拿到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工程师朱会灿,进入Google半年,一个人就推出了Google的图片搜索。这不光包括研究算法写程序,还包括架设和管理服务器等杂活。同样的工作今天即使在Google,也需要20个人忙一年。Google今天云计算基础的GFS和MapReduce技术,从设计到实现一共就三四个人,干了两年。而同样的事情微软公司投入了上百人做了五年左右的时间。我到Google的第一天,当时主管工程唯一的副总裁韦恩·罗森给我打了个比方,介绍Google是如何“培训”新员工的:“我们教你游泳的方法是,第一天就把你扔进游泳池,说,去游吧,你就会游了。”这就要求每个人都得是游泳的天才。
早期Google的方方面面都是如此。当Google有了一个小小的工程师队伍时,就需要一个管理者。佩奇和布林找到了他们在斯坦福的学长,圣巴巴拉加州大学(UC Santa Barbara)的教授、面向对象设计的专家乌尔斯·霍尔斯(Urs Hölzle)来主管工程。霍尔斯当年正在斯坦福做学术休假,考虑到这样可以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他便答应了。霍尔斯一来,便带来了他的学生和该校其他的教授,将Google工程师的队伍扩大了一倍。霍尔斯精力过人,他一到Google就管起了一大堆的事。他马上将Google搜索推向非英语用户。这件事只用了一两个工程师就完成了。因为缺人手,霍尔斯自己当系统管理员,直到Google有了400人时,每个工程师工作的账户还是由霍尔斯兼管。
出生在德国的霍尔斯对工作的质量要求极高,他发现当一个网站服务器数量多到一定程度后,永远有一些服务器会处于宕机状态,易然可以将用户请求转到别的服务器上,但如果衔接得不好,用户体验就不好。而服务器之间、数据中心之间的服务请求如何转移,里面大有学问。以前的互联网公司不管多么大,都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工程师们觉得这不是一个技术活。霍尔斯让他的一个学生来解决这个问题,要求做到从监控到流量的转移完全自动化。他的那个学生开始也觉得这个工作太没有技术含量不愿意做,霍尔斯指出这不仅很有意义,而目很有研究价值,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就说明可以用廉价、质量稍差的服务器(比如PC)提供出和那些昂贵的高稳定性的服务器(比如IBM和太阳公司制造的大型服务器)同样可靠的服务。霍尔斯最终说服了他的这位学生接受这项工作,后者不负众望解决了问题。霍尔斯和他的学生解决的这个看似细小而又没有技术含量的问题,实际上恰恰是其他公司难以提供和Google同样稳定的服务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它使得Google可以倬用最廉价的服务器,运营成本比行业的其他公司低很多。霍尔斯后来是主管Google的基础架构(包括全球网络架构、超级数据中心和云计算)、企业级服务和研究院的高级副总裁。Google著名的工程师迪恩和戈马瓦特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他的下属,并在他支持下开发出第一个版本的云计算工具。
霍尔斯具有极强的总结和概括能力。2012年我从腾讯回到美国,最初和我接洽的就是霍尔斯,我和他谈了一个小时,说自己回到Google后想做的事情。他说他需要同佩奇和(主管Google+的高级副总裁)冈多特拉谈,两天后正好他们要开会,当然可能他只有一分钟讲我的事情,为了确认他对我的想法理解无误,他用30秒钟概括了我的想法。我听了他简明扼要的几句话后,很为他的总结和概括能力折服,因为即倬我自己也难以概括得那么好。
不仅在工程上如此,在其他部门的Google早期员工也个个是精兵强将。在还没什么名气时,Google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客户很少选择Google的产品。这是所有新兴小公司都会遇到的问题,当它们把很好的产品展示给大客户时,大客户出于谨慎,总是希望小公司能证明它们的产品在同样规模的客户中成功使用过。这就陷人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中,很多小公司永远迈不出这一步。Google很幸运地请到了原来网景公司的销售副总裁科德斯坦尼来主管当时不到10个人的Google的销售业务。出生在伊朗的犹太裔科德斯坦尼是难得的销售天才,他在网景公司时不到一年就将该公司的销售额提高了两三个数量级。他来到Google后马上就创造了奇迹,成功拿下雅虎的搜索服务合同,当时Google成立刚一年多,从此Google名声大震。继雅虎以后,科德斯坦尼率领只有几个人的销售团队又一举拿下了美国在线的搜索和广告业务,并确立了Google在搜索市场的主导地位。科德斯坦尼为人坦诚,很让商业伙伴信赖,但他的绝活却是虎口拔牙。2003年,雅虎选择了Google的竞争对手Overture作为搜索广告供应商,一般来说它的日本分公司日本雅虎很自然地会和总公司保持一致。但是,科德斯坦尼居然拿下了一半日本雅虎的生意,这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这一方面是靠科德斯坦尼个人高超的销售和谈判技巧,另一方面得益于工程部门密切的合作和高效率。外界对于Google的成功一般归结于领先的技术,这的确是主要原因。但是Google的营销能力也是同行业中数一数二的。如果说科德斯坦尼有什么销售的秘诀,那主要是他的亲和力和真诚,他总是让买方觉得放心。
Google非技术部门的另一位传奇人物是首席律师戴维·德拉蒙德(DavidDrummond)。德拉蒙德通晓财务和多国法律,而且是非常老道的谈判高手。德拉蒙德保证了Google在所有的合同中几乎从来没有吃过亏。直到Google上市前,几乎所有的合同都需要德拉蒙德最后敲定。在签署大合同前,德拉蒙德都会重新谈判一次所有的细节,将Google的利益最大化。Google的利润率很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有德拉蒙德这样的人为公司节省了大的开支。德拉蒙德是Google上市谈判的两个负责人之一(另一位是CFO),面对华尔街生意场上的老油条们,德拉蒙德居然将那些投资银行的承销上市利润压到了最低,而一些大银行竟同意免费为Google服务。
Google早期的员工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每一个人的故事都能写一本书。正是靠着这一个个精英,Google才能创造历史。Google的创始人和执行官们并不同意三个臭皮匠能凑成一个诸葛亮的说法,在他们看来,再多的臭皮匠也起不了诸葛亮的作用。Google前工程副总裁罗森毫不讳言地宣称,我们只需要天才。而能够找到各个部门这么多的天才,易然Google在吸引人才方面有成功的地方,但也有很大的“幸运”因素。由于Google很明智地没有在互联网泡沫高峰期疯狂地扩展,而是实实在在地、低调地做好自己的搜索引擎,早期烧钱的速度非常之慢。2000年,Google没有急着上市,避免了绝大多数互联网公司大起大落并目最终关门的厄运,同时最早期的优秀人才没有拿了钱就走掉,因此Google的骨干完好无损。当绝大多数互联网公司都关门时,拥有足够资金的Google不仅逃过一劫,而目一下子成为了全世界优秀人才的避风港。这些人至今仍是Google的中坚力量。
Google以善待人才出名,对于每一个有缘加人Google的人,Google的创始人和执行官们都给予由衷的欢迎和充分的信任,并且让每一个人都成为Google的拥有者。施密特说得很好,Google不是我的公司,不是拉里和谢尔盖的公司,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公司。而每一个人也实实在在地把自己当成公司的主人,而不是雇员。在这个基础上,Google实行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路线。大多数公司都是由执行官们制定战略规划,然后下到各级管理层,主管们负责执行,而下面每个员工则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在这种管理前提下,一个部门的主管有着很大的人事权力,包括人员的录用和提升。Google和大多数公司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截然不同,它将日常运作改成自下而上的。它鼓励每一个员工开动脑筋,提出自己能够发展公司的想法。事实上这是一道Google的面试题,“你认为如何可以改进Google”,或者,“你来了以后将如何倬我们变得更好”。这样,每个人都主动地开始工作,并提出自己的想法。当然,一个公司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目标,不能任何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自下而上的想法就要汇集到管理层讨论,有些获得支持并得到实施,有些不切实际的就予以搁置。这样的群众路线保证了每个员工能最大限度地为公司出力。这时管理层的工作就相对简单了,因此Google公司的结构非常平一—每个人隔不了几层就能够见着CEO了。同时,主管们的权力也受到下属的制约,他们可以否决录用某个不合格的人,却无权录用自己认为合格而同事们不喜欢的人,同时,他们可以决定不提升某个下属,但是不可能提升某个和自己关系好而同事们不看好的人。
Google的这种管理模式要求每一个人都有很高的水平、很高的自觉性和很高的热情。因此Google必须严格挑选每一位员工,而不能鱼龙混杂地先招进来一大堆人,然后让主管们去发挥自己的“管理艺术”。在Google,每一个主管都有几十个直接下属,如果录用了两个经常惹麻烦的下属,或者一些能力较差的人,他们的管理艺术再好,也难以有时间将这个团队管好。Google鼓励每一个人成为英雄,它希望每一个人都做出对公司有很大正面影响的贡献,而不只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工作,并目它给予成为英雄的人很高的奖赏。
为了吸引优秀的人才,Google可谓是竭尽全力。2002年底加盟Google的罗伯特·派克(Rob Pike)是世界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他是贝尔实验室UNIX之后的操作系统Plan 9的主要开发者,以及第一个开发出基于UNIX的视窗系统的工程师。为了吸引他的加盟,Google不仅给他个人一个很具吸引力的薪酬福利包,而目给了他的小孩不少股票期权,“以便他将来不会为大学学费发愁”。派克加人Google后,改进和统一了整个公司的日志系统,并目发明了日志查询语言Sawzall,它被称为Google云计算日志工具Dremel的前身。后来,他和汤普森(UNIX的发明人之一)一起发明了GO程序语言。
每一个成功的公司都有很好的管理经验,这些经验只能参考不能照搬,Google的也是一样。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讲,照搬这种管理方式一定会乱了套。
5 绝代双骄
在很长时间里,佩奇和布林都跟大家一同吃晚饭。在饭桌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同事,会谈各自的生活。佩奇非常喜欢研究各种公司,从他愿意学习的大跨国公司到Google也许会感兴趣的几个人的小公司。偶尔佩奇会拿着一沓子他正在研究的公司的资料,和大家聊他的研究心得。
当然,光靠友好和善不足以办好公司。佩奇和布林虽然年轻,却处处表现出知人善任的用人艺术,对技术发展准确的判断和独到的商业眼光。佩奇和布林遇到的第一件麻烦事就是如何动员那些资深的“干将”加入Google。Google的第一任工程副总裁罗森和我讲了他进Google的经历。罗森原来是苹果公司的副总裁,开发了麦金托什的前身,后来在太阳公司当主管硬件的副总裁,和主管软件的施密特是太阳CEO麦克尼利的左右手。之后他自己的公司被收购,暂时处于赋闲状态,佩奇和布林马上找上他来主管Google的工程部。Google两位创始人及主要负责人与罗森会谈后对他都非常满意。但是这时罗森向佩奇提出了几个问题,并直言如果佩奇不能给他满意的答案,他不会加盟Google。佩奇给他看了一条曲线和一些东西(很抱歉在这里我必须保留细节),佩奇向他证明了Google的生意将长期近乎指数增长。罗森看过后非常惊讶,他后来讲,我当时就感觉,只要能做好,Google的生意就像印钞机一样,可以无止尽地发展,他马上就决定加盟Google。
Google成功的直接原因是通过关键词广告打开了互联网的广告市场,而策划和实施这个项目的便是佩奇。佩奇在整个关键词广告系统的开发过程中体现出超人的远见和管理能力,很让投资人佩服。很多人认为Google的成功是凑巧“蒙对了”搜索广告的业务,由此盈利并快速成长,这种说法多少有些机会论。《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则认为因果关系应该反过来,是Google将搜索广告业务变成了金矿。
微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盖茨对于个人电脑发展方向的把握,并引导整个行业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而在互联网时代,佩奇和布林对于互联网的发展方向把握得比其他公司的领袖更准确。更重要的是他们将用户倬用互联网的习惯从浏览转向了搜索,在这新的游戏规则下面,Google抢到了和以前门户网站竞争的制高点。他们确定了Google产品设计的指导思想必须突出搜索,淡化浏览。要是强调了浏览,必然把用户推到门户网站去。后来雅虎与微软MSN和Google拼搜索,实际上是“着了Google的道儿”,因为一旦拼起搜索,就必须遵守Google制定的游戏规则。现在,搜索对于网民越来越重要,这和佩奇和布林看似不经意实际上是刻意改变网民上网的习惯有关。当搜索变得越来越重要后,搜索广告也就越来越值钱,这就是在2007年Google以不足雅虎的浏览量,却产生了雅虎两倍的利润的原因。
2003年Google正式的CEO施密特上任后,布林和佩奇不再需要操心公司运营的许多具体事务,他们俩便抽出时间更多地思考公司发展的大方向。至今他们大的决策都比较成功。2005年,除了Google、雅虎和微软三家大的搜索引擎外,还有两个搜索量不容忽视的公司美国在线和Ask Jeeves。微软想通过赔钱赚吆喝的办法从Google手中抢走美国在线,但是Google在最后一刻以注资美国在线10亿美元的方式击退微软,这是需要准确的判断和魄力的。这样,便拖延了微软进人搜索广告的时间。接着,Google抢先微软收购YouTube,并目拿下MySpace的广告经营权。至此,Google将微软和雅虎以外全球所有大流量的网站的搜索广告全抢到手里,并目在互联网2.0上完成了非常漂亮的布局,在5个互联网2.0的主要公司MySpace、YouTube、Facebook、Orkut和Blogger中,Google拥有三家一一YouTube、Orkut和Blogger,同时有一家合作伙伴MySpace。要不是因为Facebook开价太高,Google也打算注资了。也许是吃了没有投资Facebook的亏,当Twitter开始风靡美国时,Google马上和它达成合作。作为Google最大的股东和决策者,佩奇和布林处处显示出超人的商业头脑和准确把握新技术的能力。正因如此,佩奇和布林在Google高管和老员工中的威信一直极高。
6 感谢神,今天是星期五(TGIF)
7 不作恶
有些时候,和没有情怀的人谈情怀,简直就是鸡同鸭讲。对于“不作恶”(Don’t be evil)这条Google不成文的口号和行为准则,很多人是持怀疑和嘲讽的态度,而不是敬佩,但是“不作恶”确实是Google所倡导和坚持的,也是它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和尔虞我诈的商业竞争中,能提倡不作恶并目一直做到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不作恶”并不是佩奇和布林提出来的,而是两位早期的员工保罗·布克海特(Paul Buchheit)和阿米特·帕特尔(Amit Patel)最先提出的。布克海特是Google的Gmail的发明人,现已离开Google,成为独立天使投资人。帕特尔是一位数学家,是Google Trend的发明人,也是面试我的几个人之一。我到了Google后发现帕特尔居然和CEO施密特坐在一间办公室里。作为普通工程师,帕特尔的工作和CEO没有直接关系。后来才知道这是帕特尔自己要求的,而施密特就答应了他。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什么是不作恶,用中国的古话讲就是要做正人君子。当然,不作恶反映在商业上,就是要公平地和对手竞争,而不采用非正常的手段。2002年,微软MSN除外的主要门户网站都采用了Google的搜索引擎,只有微软还在采用长期亏本、摇摇欲坠的Inktomi公司的服务。当时Inktomi的市值只剩下一亿美元,比巅峰时掉了99%,很多业界的人都认为这时Google如果买下Inktomi并关闭其服务,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垄断整个搜索业务,但是Google没有这么做。身在硅谷的Google深知很多硅谷公司深受垄断导致的恶意竞争之苦,整个硅谷当时对蓬勃发展的Google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和Google的合作来反抗垄断。如果Google采用这种易然合法但却是恶意的收购手段来清除对手,将令整个硅谷失望。所以,Google宁可让雅虎将Inktomi买走并成为自己在搜索领域的对手,也没有做损人利己的事。Google的这种君子之风,日后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几乎硅谷所有的公司都将Google视为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当Google推出自己的软件下载包(官方称呼是Google软件精选)时,Google找到很多软件公司,希望它们将自己的软件通过Google免费提供给用户,包括Adobe、赛门铁克等多家知名的软件公司都非常配合,并答应了Google的要求。即使是Google主要的竞争对手雅虎,在遇到困难时,也会向Google求救。这样Google在整个IT领域,除了一家公司以外,没有任何大公司与它为敌;而它的那个对手,在整个IT领域,几乎没有一个大公司朋友。
不作恶,还表现在做事的客观和公正上。这首先反映在Google对待搜索结果的排名上。搜索结果的排名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网页和查询的相关性及网页本身的质量。Google有很多科学家和工程师研究“相关性”问题,而佩奇和布林发明的网页排名(PageRank)算法是解决后一个问题的。当然,算法总免不了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Google的网页排名也不是十全十美的。针对这种情况,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手工把明显的错误改过来。很多搜索引擎就是这么做的,但是Google没有。Google的创始人佩奇和布林知道,一旦开了手工调整搜索结果的先例,以后就难免不依照个人的好恶对网页进行主观的排名。从长期来看,这样将倬搜索引擎失去公正性,并失去用户的信赖。因此,Google宁可让有些查询给出不是很相关的搜索结果,也拒绝人为调整。为了做到尽可能保证大多数查询结果能让用户满意,Google长期在研究和工程上投人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不断改进搜索排名算法。
当Google的搜索引擎变得非常流行后,很多公司找到Google,愿意出钱将自己的搜索排名在Google的结果中往前靠,但是Google坚持搜索排名不出售的政策。如果想通过Google的流量来做广告,Google是非常欢迎的,但是,Google会在页面中注明哪些是广告商的链接,哪些是搜索结果。很多人和公司认为Google的这种做法实在有些傻气,在他们看来,Google将一些愿意出钱的商家的排名往前提,能多一份收入,商家们也高兴,岂不是两全其美?然而,Google的创始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说:“我们的用户在做决定时相信我们提供的信息,是因为我们的搜索结果是我们用已知最好的算法产生的,它们公正而且客观,并且没有受到金钱的影响。我们在搜索结果旁边也显示广告,但是我们总是尽量要让广告和查询相关,并明示这些是广告。就如同在严肃的报纸上,文章的内容是不受任何广告商影响的。我们的信条是让每一个人能够访问最好的信息,而不只是付费广告商提供的信息。”Google的这种做法在短期失去了一些来得很容易的钱,但是却倬它在网络搜索中的市场份额不断地增长。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为什么Google能够洁身自好?因为它的创始人、执行官和大部分员工都懂得,要想长期发展,就必须在整个业界、在大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并赢得大家的信赖。Google的创始人非常佩服巴菲特追求长期发展的眼光,并目在Google日常工作中运用了巴菲特的很多做法。巴菲特在经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时,选定了一家银行的总裁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巴菲特有一次公开讲述了他选择芒格的主要原因。那时芒格为很多有钱人打理财务,在一次金融风暴中,全世界所有投资人都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些心慌意乱的投资人通知芒格,希望把自己的投资撤出来。易然芒格和大家讲,根据他的经验和判断,损失是暂时的并目很快就能弥补回来,但是很多人因为害怕今后损失更多,还是宁可损失一些投资也撤资了。果然,过不了多久股市的大牛市就来了。没有撤资的人不仅弥补了损失还赚了不少钱,撤资人的损失当然就永远不可能回来了。但是,芒格依然补偿了那些撤资人的损失!这种风格在尔虞我诈的华尔街简直是异类。巴菲特就是通过这件事觉得芒格是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人并选中了他。这两位投资大师在以后的几十年合作得亲密无间,共同创造了伯克希尔–哈撒韦每股12万美元天价的神话。Google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在Google早期,它为了谋求雅虎的支持,同意让雅虎在一定时间内以很低的价钱购买自己的股票,这个价钱现在看来近乎是白给。但是,互联网泡沫破碎后,雅虎并不看好Google,放弃了低价购买Google股票。等到Google快上市时,雅虎发现如果当初购买Google的那些股票,自己将多出上亿美元的投资收人,于是找到Google,希望还能以当初的价钱收购Google的股份。从法律上讲,Google没有这个义务把雅虎放弃掉的股份还给雅虎,但是,Google在和雅虎谈判后,还是给了雅虎不少补偿。
Google不作恶的做法,其实是它长期发展的重要保障。
8 不败的神话
9 秘密军团
也许是尝到了“杀鸡用牛刀”的甜头,Google不仅工程师偏向于用博士,连产品经理也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名牌大学的MBA到Google面试产品经理不成,搞不清楚这些职位都被哪些大学的MBA抢走了,后来他们发现,Google更喜欢找一些计算机专业的博士而不是名牌商学院的MBA来当产品经理。Google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让一个工科博士来做产品经理很容易和工程师沟通;其次,Google非常相信工程师们的创造力,也相信这些工程出身的产品经理有着同样的创造力。
要找到并留住大量肯动脑又肯动手的博士,并目让大家安于从事看似普通的事并不容易,这是Google尽量创造最好的工作环境,提供尽可能多的福利和自由的工作时间的结果。
迄今为止,Google在招人和用人上都非常成功,但是也带来一些隐患。主要反映在并不是所有能人来到Google后都能发挥最大的作用,造成了人才的浪费。同时,为了满足这么多聪明人做自己愿意做的事这一承诺,搞出了很多意义不大的小项目。很多媒体和投资人对Google的这种问题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担心Google重蹈当年苹果的覆辙。但是要兼顾调动员工积极性、鼓励创造性并集中精力在核心业务和重大项目上,对任何公司来讲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10 云计算和数据中心
11 新气象
12 移动互联网时代
13 进攻,永远是最好的防守
14 佩奇新政
15 未雨绸缪
16 成败萧何
Google的很多特点,追根溯源都可以归结为工程师文化。佩奇在Google上市后不久就对全体员工讲,Google会永远保持工程师文化,工程师在公司里会永远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可以说,坚持工程师文化是Google的成功之道,但是正如世界上不存在只有正面没有反面的纸一样,也不可能存在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企业文化。Google的工程师文化在让它不断走向胜利时,也导致了它的不少失败。而这其中最大的失败就是和亚马逊的云计算之争。
最初提出云计算概念的,是Google、亚马逊和IBM三家公司。从技术上讲,Google领先于亚马逊,但是Google在云计算的业务上步伐一直落后于亚马逊。这里面有商业模式本身的原因,也有企业文化的因素。
简单地讲,Google、微软以及中国的华为这类公司以工程师文化为主,因为盖茨、佩奇和布林以及任正非,他们都是工程师出身,会注重技术上的研发投入,热衷于做出技术好的产品,但有些时候,产品体验却做得不算好。苹果、Facebook和腾讯等公司则是以产品经理为主的企业文化,工程师围着产品经理转。它们的产品用户体验流畅,至于背后的技术好不好,就看工程师的自觉性以及公司领导对质量要求有多高了。乔布斯在的时候,苹果的产品以质量好著称;乔布斯不在了,虽然产品设计得不错,但是小毛病不断。这两类公司有时候都会有一个短板,那就是商业推广上赶不上单纯靠商业起家的公司,比如亚马逊和阿里巴巴这类公司,它们的企业文化是销售文化。当然,阿里巴巴的人可能觉得自己也有工程师文化,但是,一个企业不可能有两种文化,这就如同脚踩两只船的人一定会掉到水里一样。除了阿里巴巴,世界上还没有哪家大的互联网公司要公布双11、黑色星期五(美国感恩节后的周五)或网购周一(Cyber Monday,美国感恩节后的周一)销售额,易然每家电商公司那几天都处在全年销售额最高峰。这个细节足以说明阿里巴巴对销售额的看重。亚马逊的情况也类似。
不同的企业文化决定了他们的竞争优势或劣势,如果技术处于同等水平上,那么无论是工程师文化还是产品经理文化的企业,都难以和销售驱动的企业竞争。因此,以技术为导向的企业需要建立足够高的技术壁垒,以产品为导向的企业需要不断在产品创新上拉开与竞争对手的距离。对Google来讲,不幸的是,它和亚马逊基本上处于同一技术水平,那一点点技术差异不足以带来商业上的优势,而一直习惯于在微薄利润下生存的亚马逊,更有能力在云计算这种微利行业中生存。
世界上再优秀的企业,都很难兼顾这样的三方利益,即员工利益、消费者利益,以及投资人利益。这就如同不可能既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还让马儿不掉膘一样。如果一个行业发展得很快,这个蛋糕还比较容易分。但是,对于Google或亚马逊这种遭遇了诺威格宿命的大企业,不可能总让业绩翻番,这就必须在员工、消费者和投资人之间做一个选择了。
很多公司选择了首先维护员工的利益,比如著名的星巴克公司就选择了员工优先,这和公司老板舒尔茨小时候的经历有关。舒尔茨的父亲过去在一家企业工作时因为脚伤无法上班,那家企业对员工极糟糕,让舒尔茨父亲没有收人,还得不到救治,舒尔茨从此下定决心,如果将来办公司,就一定要做到员工优先,他后来就是这么做的,在星巴克哪怕临时工都有医疗保险。舒尔茨时常来中国,每次和员工开会就是讲说心灵鸡汤故事,鼓励一下大家,从来不骂下属。然而,舒尔茨对顾客可不算好,首先星巴克大部分的咖啡品质并不好,是靠香精糊弄大家;其次,舒尔茨公开说不欢迎特朗普的支持者来喝咖啡,而后者也不示弱,说要天天带着咖啡去星巴克蹭免费的糖和牛奶。和顾客关系搞到这个地步,在全世界都罕见,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星巴克成为好公司。而Google、腾讯和基因泰克等公司恰好也是这一类员工利益优先的公司。顺便说一句,Google已经很多年被评为美国最佳雇主,之前基因泰克是曾经的美国最佳雇主。
当然,也有公司选择顾客优先,比如亚马逊、阿里巴巴、运通卡,等等。亚马逊对员工非常抠门,我在Google的一个同事来自亚马逊,现在是搜索部门的一个副总裁,来Google时是我面试的。等他到Google上班后我问他对亚马逊的印象,他只说了一个词:Frugile,即节省的意思。当然他比较体面,不说原雇主的坏话,但他要表达的是亚马逊抠门。我的很多朋友在亚马逊工作,抱怨福利很差,特别是医疗保险不行,但是大家看在公司股票疯涨的份上,就不那么在意福利了。不过,亚马逊对顾客,无论是商业伙伴还是个人,态度都很好,它的很多工作就是为了方便顾客。类似地,阿里巴巴在顾客利益和员工利益出现矛盾时,就只好牺牲员工利益了。但是,无论如何,它们都是好公司,只不过是另一类好公司。
当然,还有专门对投资人好的公司,这些我们就不多说了,巴菲特投资的公司都属于这一类。
易然从长远来讲平衡这三方面的利益很重要,但是没有哪个公司能够脚踩三只船而不落水,要想兼顾三方,结果就是三方都服务不好,因此,坚守自己价值观的企业通常会保证一方的利益。当然,在短期商业竞争中,无疑是客户优先的公司更有优势。公平地讲,过分强调工程师文化,甚至有点把工程师捧上天的Google,在满足企业级客户需求方面,明显做得不如亚马逊好。著名的大数据医疗公司“人类长寿公司(Human Longevity)”有大量的云计算任务,它过去的首席科学家是来自Google的人工智能专家、机器翻译的负责人奥科博士。照理说,人类长寿公司应该优先考虑倬用Google的云计算才对,但是奥科博士告诉我,亚马逊提供了更好的服务和价格,而目配合他们的工作,于是他们自然就选用亚马逊的服务。硅谷另一家大数据医疗领域的明星公司圣杯公司(Grail),创始人胡贝尔(Jeff Huber)是Google过去主管广告的高级副总裁,工程副总裁科斯是Google主管全球架构的副总裁之一,主管机器学习的两位负责人也来自Google。照理说这家公司总该用Google的云服务了吧!不,它依然倬用了亚马逊的AWS云服务,因为亚马逊为他们公司专门配备了一个20人的工程团队,帮助解决与计算相关的所有问题。连Google自己的员工创办的公司都不使用Google的云计算服务,说明Google的云计算相比亚马逊有了大问题。
当然,Google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佩奇请来善于做企业级市场的VMware创始人格林女士(Diane Greene)出任主管云计算的高级副总裁。VMware的特点和亚马逊很相似,它们都属于市场驱动的公司。格林女士掌管Google云计算后,确实大幅提高了Google云计算的市场占有率,但是她很快遇到了瓶颈,因为她的那些快速占领市场的手段用尽之后,还是无法调动工程师团队按照她的意愿开发新的服务和改进现有服务。我在与过去Google的同事以及Google现任高管的接触中了解到,大家对她的评价完全是负面的。客观来说,这些评价不是很公平,但是,有着销售驱动基因的格林无法融人Google的工程师文化,显然是事实。格林为了确保她的想法能够得到实施,找来她一位“闺蜜”、一位颇有名气的技术专家在云计算部门担任要职,结果她们一同被大家诟病,最终格林女士离开了Google,而她的那位朋友也随即离开。易然不能确定是不是给格林更多的时间,她就一定能扭转Google云计算的被动局面,但是对她本人的不接受,确实是Google工程师文化的一个弊端。
除了格林,以产品为导向的冈多特拉,以及其他一些外来的高管都难以在Google生存,这显示出Google固步自封的一面。正是因为过度强调工程的基因和工程师文化,Google很多原本很有前途的项目,包括Google眼镜和人工智能,都是只开花不结果。可以说,Google依靠纯正的工程师文化和技术基因起家,并目在竞争中长期无往不利,但是也因为这个基因太强大,令Google缺乏灵活性,缺乏在新领域的适应性。或许Google在拆分成数家独立的公司后,在某些新的公司里能够孕育出新的企业文化。
结束语
Google的前CEO施密特在会见中国的政府官员时总是讲,Google是个奇怪的地方。也许是因为Google的年轻人太多,他们不大懂得传统也不拘泥传统,只要认准了对公司对社会有用,就大胆去干。庆幸的是,以施密特为首的Google的执行官们非常开明,任由年轻人自由发展,才有了无数的创新。Google中国的前总裁李开复总是讲,Google是一家令他震撼的公司。其实,Google只是硅谷生产关系和文化的浓缩,Google的所有现象,在硅谷其他公司或斯坦福大学,都能找到类似的痕迹。
Google大事记
1998 Google成立。
1999 美国最大的两家风险投资公司KPCB和红杉资本同时投资Google,这是这两家公司第一次同时投资一家初创公司。
2000 雅虎采用Google的搜索引擎。
2001 Google推出搜索广告系统AdWords,并于当年第4季度实现盈利;同年,埃里克·施密特成为Google的正式CEO。
2002 美国在线采用Google的搜索引擎和广告系统,Google占到全球搜索流量的70%。
2003 Google第二个广告产品AdSense上线。
2004 Google采用竞拍的方式上市;同年Google的革命性产品Gmail和Google Earth上线。
2005 Google中国公司成立。
2006 Google在线支付产品Checkout上线,效果极差,成为Google第一款失败的主要产品;同年Google收购YouTube。
2007 安卓联盟成立。
2008 第一款基于安卓的手机由HTC推出,但是销量一般;同年Google推出Chrome浏览器。
2009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Google第一次裁员,但是很快回到增长的轨迹;同年随着摩托罗拉Droid手机的上市,安卓手机操作系统获得巨大的成功。
2010 Google的手机操作系统安卓市场占有量超过苹果的iPhone,浏览器Chrome也从微软手中夺得15%的市场份额,但它在社交网络上一直不敌Facebook。
2011 共同创始人佩奇接替施密特成为Google新CEO,同年Google推出Google+社交网络服务。
2012 Google收购摩托罗拉移动公司,2014年又将它出售给联想公司。
2014 Google将名称改为Alphabet,Google成为它旗下的一家控股公司。
第19章 科技公司的吹鼓手 投资银行
在科技公司背后,存在着左右它们发展,影响其商业行为的金融力量。对于尚未上市的公司来讲,这种金融的力量主要来自于风险投资;而对于上市公司来讲,这股力量则以投资公司或投资银行为代表。若没有投资银行,科技公司很难在金融市场上融资,开展并购和分拆。我最初动笔写这一章是在2007年,当时上一次大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发生。等到2008年底我准备在谷歌黑板报上发表本文初稿时,金融行业已经发生了巨变,随后各种危机一个接着一个,世界金融市场的格局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在我动笔之初,美国被称作“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的投资公司主要有五家,即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高盛(Goldman Sachs)、美林(Merrill Lynch)、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等我完成本书第一版时,只剩下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两家独立的投资银行了。在金融危机之后,投资银行数量减少,影响力也有所减弱。也正是在那之后,科技公司自身的金融力量得到了巨大的增强。不过,即便如此,以投资银行为代表的华尔街对世界经济和生活的重要性依然不可小视,而目比绝大多数人所理解的要大得多。在中国,情况也类似。
金融资本除了力量大之外,另一个特点则是贪婪。像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这样的公司,它们是微软、Google和雅虎这些公司上市时的承销商(Underwriter),之后的股票持有者。如果遇到拆分和并购,它们还会是资本运作游戏中的主角。我把投资银行比作“吹鼓手”,是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吹捧一些科技公司,制造泡沫,这样有利于新产业的繁荣。“吹鼓手”显然不能算是褒义词,对科技公司从捧杀到打压,变化只在一念之间。他们中间甚至有一些腐蚀者,目的就是加速过气企业的衰亡。
风险投资和投资银行易然同样握有资本,但是对企业来讲性质完全不同。前者几乎全是正向的作用,是企业可以依赖的朋友。后者则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会锦上添花,用不好则会玩火自焚,正所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点,每一个IT行业里的决策者都必须很清楚。
1 美国的金融体系
……
美国的金融公司五花八门,非常之多。2008年,美国证监会为了救股市,列出的股票不能做空的上市金融公司居然高达800家之多,而美国的银行更是多达8000家,平均一万多个家庭就有一家银行。这些公司大致可以分成几类。
商业银行(Commercial Bank),这是老百姓最熟悉的传统银行,中国包括四大商业银行在内的几乎所有的银行都属于这一类。在美国,著名的商业银行有花旗银行、富国银行(Wells Fargo Bank)、摩根大通银行(J. P.Morgan Chase Bank,以前叫大通曼哈顿银行)和美国银行(Bank ofAmerica),它们都是或曾经是道琼斯30家工业指数中的公司。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开始,到里根上台以前,商业银行只能发放商业贷款和房屋贷款,不能买卖股票。但是近30年来,美国政府放宽了银行业的限制,很多商业银行同时又是投资公司,比如美洲银行旗下的美林证券,以及花旗过去的花旗美邦(Smith Barney)都是很大的投资公司。摩根大通银行则身兼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二职。大银行中只有巴菲特控股的富国银行安分守己,因此在上次金融风暴中它损失最小,并随后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商业银行。
投资公司,虽然在过去中国的媒体又称它们为投资银行或投行,但是直到2008年10月,它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因为既不能接收存款,也不能向联邦储备银行借钱。它们主要替客户买卖有价证券、期货、不动产和任何有价值的商品。因此,在英语里它们过去确切的叫法是投资银行业企业(Investment Banking Firm)。不买卖股票的人对这一类公司就不大熟悉了。这些公司中最著名的是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本来还有美林证券和雷曼兄弟等几家,但如前所述,它们全都关门了。这些公司是股市上翻云覆雨的主力军,俗称庄家,对科技公司的兴衰影响最大,它们不仅抬高或打压科技公司的股价,而且可以左右科技公司的并购和分拆的成败。比如前面提到的AT&T分拆案、惠普和康柏的并购案,以及没有做成的微软和雅虎的并购等,背后都有投资公司插手。除了美国有投资银行外,欧洲和日本等也有大的投资银行,比如苏黎世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CSFB)和瑞士联合银行(Union Bank of Swiss,UBS,它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一体)。2008年10月后,美国将这些投资公司的性质由原来的公司转变成真正的银行,这样美联储才能合法地出手相助。
此外,巴菲特的旗舰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是一个影响力极大但非常特殊的投资公司。它不仅通过大幅度参股的形式控制着富国银行、运通公司(世界第三大信用卡品牌)等一批金融公司,还运营和控制着很多优质的传统型企业。不过,巴菲特从不投资快速增长的科技公司,因此伯克希尔–哈撒韦对科技发展影响甚微。
共同基金公司(Mutual Fund),这类公司特别多。大的如富达基金(Fidelity)和先锋基金(Vanguard),掌控着美国所有的退休账户(401K )和全球大量财富。到2018年,富达基金所管理的各种资产,包括不动产,总计将近7万亿美元。而小的共同基金可能只有几十人,只管理几亿美元。总的来讲,共同基金的目的是为了投资而不是炒作。但是它们常常是一些科技公司投票权最多的股东,盈利好就追捧它,遇到困难时便给它施压,要求它裁员或减少开支,因此对科技公司的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对冲基金(Hedge Fund),包括著名的文艺复兴技术公司(RenaissanceTechnologies),以及索罗斯和罗杰斯的量子基金(Quantum Funds)。由于美国严格限制共同基金公司做空股票和期货,很多华尔街的大鳄觉得这些规定限制了自己炒作的才华,于是办起不是出于投资目的而是专门靠炒作挣钱的对冲基金。虽然对冲基金规模较小,全球只有一万五千亿美元的规模,但是由于它们可以卖空股票、期货和货币,并且可以通过借贷用自己码金(Margin)几倍甚至几十倍地买多和卖空一支证券或商品期货,力量不可低估。索罗斯等人的量子基金在1998年几乎要了东南亚国家的命,虽然索罗斯本人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文艺复兴技术公司是全球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公司,平均年收益超过30%,高于巴菲特的旗舰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在全球股市暴跌的2008年,它更是逆势而上,当年盈利80%。金融危机时,为了防止对冲基金恶意卖空,美国证监会不得不要求对于敏感的金融股,必须“借到”实际的股票才可以做空,俗称限空令。
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如之前介绍的,风险投资基金从管理和股权性质上讲是一种特殊的私募基金。不过相对全球经济的体量,风险投资基金的规模非常小,在美国从2000年互联网泡沫之后一直徘徊在每年200亿—400亿美元左右,直到2015年后,才重新突破400亿美元的规模,相比富达基金管理的7万亿美元资产,可以忽略不计。因此,风险投资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大。另一类私募基金的体量则大得多,它们通过收购公司(包括上市公司)、资产重组、重新上市(或者出售)等方式,赚取较高的利润。相比风险投资,这些基金每一笔交易的金额都非常高,动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不过他们一般不炒作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因此通常既不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也不是受害者。在私募基金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中国政府参股的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和KKR等。
资产管理公司,比如著名的贝莱德(BlackRock)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家族和机构资产高达四万亿美元。它们的主要工作包括资产配置,比如将一部分钱交给高盛等投资机构或者风险投资公司去管理,当然它们自己也做一些私募基金的事情。不过,它们并不做很多活跃的短线交易,其投资行为对股市的影响是通过高盛等公司间接体现出来的。
这些大的银行和投资公司,每一个都可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除了前面说的贝莱德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高达四万亿美元的资产,花旗银行在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峰值资产高达两万两千亿美元,投资公司高盛控制的财富高达1.4万亿美元(2017年)。2018年,富达基金和先锋基金控制的财富分别高达6.8万亿美元和4.2万亿美元。
2 著名的投资公司
2.1 高盛集团
2.2 摩根士丹利
3 公司的上市过程
一家科技公司的成功从根本上讲要看它是否代表了技术发展的潮流,要看它的运营等自身的因素。但是,华尔街对它的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当一家科技公司开始准备上市时,投资者对它的影响就从风投基金过渡给华尔街了。
风投公司要收回投资,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和早期员工要得到创业的回报,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是被收购,比如YouTube被Google收购,Skype被eBay收购。这种做法来钱快,操作简单,但是收益相对低一些。走这条路的公司往往有很好的技术,或者拥有很多用户,但又难以盈利,YouTube和Skype都属于这一种。第二是将自己的一部分股票拿到交易市场上公开出售(Initial Public Offer,IPO),俗称上市。多数盈利良好的公司基本上都走了这条路,上市不仅可以让投资人获得回报,还可以为企业的发展筹措资金。
科技公司的经营业务是科技产品和服务,而不是证券,不能自己到证券交易所去兜售自己的股票,必须交给承销商比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这样的公司来做。承销商以上市价从被承销的公司收购一定数量的股票,并且以同样的价格分配给它们的客户。承销商从上市中可以得到两笔收人,第一笔是佣金,通常是包销股票总金额即融资额的7%;第二笔是后续以上市价继续购买该公司一定股份的权利(大致等同于期权)。当然,这第二笔钱只有当上市公司股价上涨时才有意义。我们以百度公司为例,简单介绍一下科技公司上市的基本过程。
在上市前,百度需要找一家承销商,一般会跟多家承销商洽谈,找到一家自己中意的。而在谈判中,关键要确定三件事。
第一,在上市时百度公司总的市值值多少钱。上市之前百度是私有的公司,它的股票没有在市场上交易过,因此,没有人知道这家公司到底该值多少钱。百度当然希望自己作价越高越好,而承销商则希望作价适中。作价太高,它们就无法保证百度的股票会被全部认购,而且它们大量以上市价核算的百度股票期权获利甚微。作价太低,它们将拿不到什么佣金。佣金是承销商旱涝保收的钱,而它们得到的期权却未必能够最终变成利润,比如黑石集团上市时的期权基本上如同废纸。那么对百度作价高的公司是不是就一定好呢?这并不一定,因为承销商的影响力对上市的成功至关重要。最后,百度选择了由高盛(亚洲)和苏黎世信贷第一波士顿作为领投承销商,Piper Jaffray公司参与承销。事实证明这个选择非常明智,很好地平衡了公司估价和承销商影响力,并且保证了百度股价的平稳。Piper Jaffray规模很小,作用可以忽略。选择高盛和苏黎世信贷的最大好处是,这两家投资银行不仅没有散户,连小的机构都没有。这样,就不可能有任何散户和小的机构可以按上市价拿到百度的股票,所以中小投资者要想购买百度的股票,只能从高盛和苏黎世信贷的大客户手上买。而众所周知,大客户一般比小客户更倾向于长期投资而不是短线炒股套利。因此百度上市后,市场上几乎不可能有股票流通,在相当长时间里,股价肯定看涨。根据美国证监会的规定,公司内部的股票必须在180天后才能到市场上交易(相当于中国的大小非解禁)。凡是做过股票的人都有这个经验,一旦公司内部股票解禁,股价都会暴跌,这种事情一旦发生,不管上市公司在上市的头几个月股票被炒得多高,等到创始人和员工可以卖出时就贬得一钱不值了。百度找高盛和苏黎世信贷承销上市,就避免了这个问题,因为在前180天里,市场上几乎没有可流通的股票,广大的散户都得等到180天后,才能从创始人、投资者和员工手里大量购入。相反,如果百度找到美林等二流承销商,虽然作价可以高一点,佣金可以低一点,但是由于美林等公司的客户常常是众多的散户,这些散户稍微有利可图就会抛售百度的股票,对稳定百度的股价反而不利。不然,等到180天后李彦宏等人被允许出售股票时,股价就会跳水了。
和百度相反,中石油在香港的上市堪称败笔。首先它作为全球最大的融资行动之一,却选择了一家二流承销商瑞士联合银行和不人流的中信。瑞士联合银行易然是瑞士最大的商业银行,但是其投资银行的水准却跟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相差甚远,甚至不如它的同胞公司苏黎世信贷。这两家承销商为中石油作出了天价的融资股价,以至于长期持有它的巴菲特马上套现。两家的客户中有很多中小投资者(包括机构),当他们幸运地分得一些中石油的股票后,在上市的当天就抛售给了更小的散户。虽然中石油在上市的当天创下全球市值最高的纪录,但是不到半年就跌破了发行价。等到中石油自己手上的股票解禁时,已经卖不出多少钱了。
第二,上市公司融资多少。一个待上市公司的基本价值确定后,就要和承销商协商融资的额度。一般来讲,只要能卖出去,承销商倾向于多融资,这样它可以多拿佣金,而且可以打压上市价。而对于待上市公司来讲,融资太多会过度稀释股权,使得公司的总市值变小,融资不足则无法保证今后发展的资金需要。具体到百度,当时高盛等承销商按照300到400的市盈率,为它估价在6到7亿美元之间。后来由于网络搜索在2005年非常热门,百度首发(IPO)股票认购量超过发行量的10倍,高盛等承销商同意将百度的市值提高到了8.6亿美元。当时百度有2800万股,这些股票属于投资人、创始人和员工,统称为原有股东。假如公司想融资两亿美元,那么原有股东的股值就只剩下8.6–2=6.6(亿美元),每股的价钱在23美元左右。如果百度只融资2000万美元,原有股东的股票还可以值8.6–0.2=8.4(亿美元),那么每股值30美元左右。在前一种情况下,企业获得充足的发展资金,但是原有股东的利益损失很大。在后一种情况下,原有股东过于吝啬,使得公司错失很好的融资机会。最后,百度做了个折中,它在上市时将增发400万股,融资1.1亿美元,每股定价27美元。
融资过多和过少都是有危害的。融资过度,则原有股东的利益被压缩,而目短时间内流人市场的股票太多,股价很难稳定。融资过少,危害也很明显,很多公司就是因为融资不足而在经济进人低谷时缺少资金摆脱困境而关门。2000年有两家规模和水平相当的语音识别公司在美国上市,第一家Nuance融资近2亿美元,基本保证了它安全度过2001一2003年网络泡沫破碎后的艰难时期,第二家SpeechWorks融资不到1亿美元,到2002年就已现金不足,难以为继,当年就被低价收购。可以说,融资的成败决定了企业的命运。一般来讲,融资的比例应当是公司市值的10%一25%。
第三,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确定后,剩下的就是一些细节问题了,主要是百度付给承销商的佣金和今后的期权。一般来讲,著名的承销商要的条件也高。华尔街一般承销上市的佣金是融资额的7%,但是如果遇上像Google和Facebook这样强势的客户,佣金比例远远低于7%,事实上Facebook的佣金只有区区1.1%。早期的投资银行基本上是靠佣金挣钱。后来,投资银行越来越多地在上市行动中要求获得一些股票期权,以锁定上市公司今后股票上涨带来的利润。当然,如果上市公司的股票不上涨,这些期权就是废纸。为了保证那些期权将来不是废纸,承销商会尽可能地把上市价钱定得低一些,这是华尔街不成文的行规。中国有些企业家看到自己公司上市后股价上涨,就抱怨承销商定价低了,其实是不懂华尔街的行规。有些几乎不盈利,甚至是亏损的公司,之所以能在纳斯达克上市,全靠投资银行这个吹鼓手,得罪了投资银行,对上市公司自身基本上没有好处。
一家科技公司不仅要找一个能在这三个方面给予自己最有利条件的承销商,还要找好上市的时机。百度的上市时间选择得很好,它处于2003—2007年美国新一轮牛市的中间,而且是在Google上市一年后。2004—2005年,Google的股价暴涨,因此作为同类公司的百度在估价上占了很大的便宜,它的估价从最初申请上市时的300倍市盈率,在一个月里开始发售股票时,提高到500倍。这样百度实际融资1.1亿美元,比预想的多融资了4000万美元。同时,拥有百度1/4股权的创始人李彦宏一夜之间身价超过了2亿美元。高盛等承销商瓜分了大约700万美元的佣金,同时获得了40万股百度的期权。以百度当天的收盘价90美元左右计算,这笔期权价值2500万美元这次上市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投资银行帮助IT公司上市,如果后者在经营和财务上有问题,前者多少要承担一些法律风险。因此,对于潜在问题较大的公司,投资银行收取的佣金一点都不能少,甚至会拒绝为其承销上市,否则得不偿失。2010年到2011年,国内不少中国概念股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因为在经营和财务上有问题,很多都被股东告到法庭,一些甚至被摘牌,而承销上市的投资银行常常也会被列人被告。2010年一家中国的电子商务公司上市后,其CEO公开抱怨承销商估值低了,暗示从他的公司挣钱多了,这是不懂行规的典型表现,因为投资银行通过承销上市融资来挣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事实证明,承销商定的股价不是低了,而是过高。这位CEO的行为,对其他即将上市的公司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2011年后,华尔街对中国概念股在美国上市明显不如2010年热心,和这些负面影响都有关系。
4 双刃之剑
承销上市只是投资银行和基金公司对科技公司影响的开始。在上市以后,如果一家科技公司得到了华尔街投资银行和基金经理们的青睐,它的发展无疑会顺利得多,反之则艰难得多。
投资银行和基金公司对科技公司最大的支持就是直接买进该公司的股票。2004年Google公司上市后,立即得到华尔街的追捧。全球最大的基金公司富达基金,回报率最高的美盛(Legg Mason)价值信托基金(Value Trust)和最著名的对冲基金文艺复兴技术公司都大量购人Google的股票,使得Google的股价在两个多月里翻了一番。富达基金一度持有Google大约10%的流通股份。
华尔街对科技公司的追捧还可以通过提高对科技公司的评级等无需成本的手段进行。由于很多投资人无法看清一家公司未来三五年里的发展前景,需要参考金融研究部门的研究报告和股票评级作出投资决定。如果一家著名的投资银行认定某家科技公司今后几年会有超出预期的发展,那么该公司的股票就看涨。2004年底,美国证监会在Google上市的3个月后解禁了一批创始人和员工持有的股份,Google股票的流通量几乎翻了一番,股价相应下调了15%。这时,高盛公司发表研究报告,力挺Google,并上调了Google的股价预期。在报告发表后的几小时内,Google的股价暴涨10%,顺利化解了因内部股解禁而带来的卖压(Sale Pressure)。借助股价的大幅上扬,Google在上市后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的英才,迅速推出多种服务,并一跃超过雅虎成为第一大互联网公司。像Google这样华尔街眼里的明星公司有很多,包括微软公司、苹果公司、设计和制造黑莓手机的RIM公司,以及十多年前的雅虎公司等。百度公司在纳斯达克之所以能有100倍的市盈率,也全靠投资银行托盘。
华尔街会为每个科技公司定下营业额和盈利的预期。如果一个科技公司能够在连续多个季度里超出盈利预期,华尔街就会拼命提升该公司的股价。由于科技公司员工的期权占员工收人的比例非常大,因此一家科技公司的股价能否稳定增长决定了该公司员工的收人和士气高低。在2000年互联网络泡沫时代,新兴的雅虎公司之所以能够阻击微软等IT巨人的进攻,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华尔街帮它维持了高股价。
华尔街自然不是雷锋,它推高一家公司股票,并非出于帮助那家公司的动机,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因此,它不会因为喜欢哪家公司就扶持它,而是要看哪家公司在特定阶段更能给它带来利益。就说微软吧,在鲍尔默担任CEO的十多年间,其股价一直不振,因为鲍尔默十年如一日地卖软件,实在没有什么吸引人的新意,华尔街看不上它。其实,客观地讲,那十多年里微软的利润一直很高,但是华尔街给它的市盈率不到20,这在软件公司里是很低的,因为无法讲故事,吸引不了中小投资人参与炒作微软的股票。2014年新的CEO纳德拉上台以后,将原来的Office从卖软件改成卖“云服务”,这就有故事讲了,微软的市盈率被提升到30以上,甚至一度高达50。于是,这些年微软业绩提升并不大,股价倒大涨了200%,这便是华尔街的作用。
当一家公司不再有故事可讲时,华尔街就不搭理它了。而当它盈利不及预期时,就可能被华尔街狠狠地打压。本来,在股价上打压那些经营不善,或者把投资人的钱变相收人囊中的上市公司是应有的惩戒行为。但是,华尔街常常过度利用这种手段,以谋取私利。于是,达到华尔街预期,成了大多数上市公司唯一的目标。这样一来,大多数科技公司不得不制定很多短期目标以满足近期的盈利,这样很可能会影响它们的长期发展。在许多外人看来,很多科技公司的短视行为显而易见,很不明智,但是这些上市公司也有苦衷,很多是迫于华尔街的压力不得不如此。有些公司明明已经达不到华尔街的预期,只能靠合法的作假来饮鸩止渴。我们在前面“帝国的余晖”一章中提到,朗讯公司为了达到华尔街的预期,不得不贷款给没有偿还能力的公司来购买自家产品,以提高营业额。易然在几个季度里它的业绩表面上看比较漂亮,但是一旦这些借贷的公司倒闭,朗讯公司的货款就永远要不回来了,继而出现巨额亏损。在2004一2005年里,雅虎公司为了粉饰财务报表,低价售出它所持有的全部Google股份,并计入其利润。但是,当再也没有Google股票可出售时,它的利润便迅速下降,公司败相显露,股价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人心涣散,核心员工离职的速度比公司衰退的速度更快。
对于那些价值不大的科技公司,一旦它们未能达到预期,华尔街则会毫不留情地打压到底,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美国的一个财经电视频道介绍了这样一个故事。在美国有一家颇有名气的网上售货公司叫Overstock,一年的营业额大约是8亿美元。它于2002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在2005年的第二季度,它的盈利比华尔街预期的每股少了一两个美分,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小小的一两美分使得Overstock几乎遭遇灭顶之灾。一般纳斯达克公司是在收盘后公布业绩,业绩一出来,华尔街马上调低对它的评级。第二天,Overstock的股价狂泻不止,在短短的几天里,跌幅在50%以上。它的CEO帕特里克·拜恩(Patrick Bryne)在气愤之余发狠心要调查清楚此事。他经过调查发现,Overstock公司的股票被恶意卖空,卖空的股票数量是Overstock实际股票数量的十几倍。根据美国证监会的规定,抵押一定现金“借”股票卖空是允许的,但是卖出的股票一定要在三天内提供给该股票的买家。既然被卖空的股票是实际股票数量的十几倍,那么肯定有人借不到股票,也就无法按期交割。事实上,华尔街的那些卖空者根本就没打算按时交割,一些人一周后还无法交割,更有甚者到了第二年还无法交割,最终这些交易只能作废,当然华尔街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但是,Overstock公司的股价因为这种十几倍的卖空而一落千丈,公司也几乎关门。华尔街没有付出任何成本,就通过卖空一家科技公司的股票挣得暴利。在这一事件中,华尔街的评级公司对Overstock打压在先,对冲基金恶意抛售在后,配合得天衣无缝。读者不难看出,像Overstock这样的中小公司,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被华尔街攥着。可以说,华尔街是通过Overstock杀鸡儆猴,对盈利不能达到预期的公司予以惩戒。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上市的科技公司敢牺牲几个季度的盈利来换取长期发展。Overstock的CEO拜恩气愤之余,把收集到的所有材料和他在各个电视财经频道上的访谈都放到了公司网站上。拜恩本人也因为长期和华尔街裸空的基金们斗争而出名。
为了不断达到华尔街的盈利预期,几乎所有市场占有率超过一半的大跨国公司都不得不努力寻找新的增长点。这实际上是软件业务做得相当好的微软公司一定要进人互联网市场的根本原因。在寻找新的增长点时,很多大的跨国公司不可避免地盲目扩张,最后因为投资和消耗太大而转盛为衰。这种例子实在太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那么一家上市的科技公司只要盈利,是不是就可以忽视华尔街对自己股票的打压而专注于长期发展呢?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是科技公司还是个人都不是处在真空中。要想不受华尔街的影响,唯一的办法就是不上市。这就是Google和Facebook在盈利很久以后迟迟不肯上市的原因。一些很有潜力的上市公司因为某种原因,受到华尔街长期打压,这时,私募基金会出资收购该公司流通的全部股份,将它变成私有公司,经过包装后重新上市,这时新的公司常常就会从华尔街的弃儿变为宠儿。著名的计算机硬盘公司希捷科技(Seagate)就经历过这一过程。2018年,烦透了华尔街不断质疑的马斯克向媒体透露特斯拉公司有可能考虑私有化。易然后来证明他是信口开河,但客观地讲,如果有合适的人愿意接盘,这对于盈利情况并不好的特斯拉公司来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5 左右并购
除了从科技公司上市和炒作科技公司股票上挣钱外,华尔街另一大赚钱的手段就是操作公司的并购和拆分。当两家公司合并或一家收购另一家时,需要把两家公司的股票合并成一种。和上市一样,这件事不能由科技公司自己完成,而由投资银行作为承销商代理完成。当然,投资银行可以获得可观的佣金,甚至合并后的新公司的期权。拆分也是如此,每拆掉一家公司,其中的一些部门要么上市,要么和其他公司合并。投资银行也能坐收佣金。因此,华尔街希望科技公司之间经常地并购和拆分。在AT&T、惠普及后来朗讯的拆分事件中,还有惠普和康柏的并购中,华尔街都赚足了钞票。
当然,华尔街也不是一味鼓励科技公司三天两头地兼并和拆分,它们要根据自己最大的利益来做决定。由于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和基金公司在已经上市多年的科技公司中占很大的股权和投票权,它们有能力决定一次收购和拆分是否进行。我们回顾一下2008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微软收购雅虎事件,来看一看华尔街在微软、雅虎和Google的三角关系中起的微妙的作用。
……
结束语
在整个经济活动中,金融业起着血液的作用。健康的金融环境和秩序有助于科技公司成长。但是,由于金融业和巨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贪婪、投机甚至非法的欺骗行为是金融业永远也摆脱不了的阴影。一位银行家曾经说过,虽然我们的社会和商业跟一个世纪前相比有了本质的不同,但是华尔街和一个世纪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今后依然如此,因为这是人类贪婪的本性决定的。
在这样一种前提下,一家科技公司如何才能和华尔街合作得很好,让那些投资银行和基金公司成为自己的吹鼓手而不是杀手,便是一种艺术了。事实上,在美国一家上市公司的首席财务官的首要任务并不是替公司管账,而是和华尔街沟通。他应该能用财务的语言,向华尔街厘清所在公司的长远规划,让华尔街树立对公司的信心。
从好的一方面理解,华尔街对上市的科技公司追捧也好、打压也好,从客观上推进了科技行业的优胜劣汰。一家真正管理得好并目有竞争力的公司,应该抵御得住多次金融危机或投机者的恶意打压。它既要有长远的发展规划,又要能在短期内让投资人有信心,同时能很好地和华尔街沟通。另一方面,一家科技公司又不能刻意迎合华尔街的短期期望,否则它的发展会很被动。这样的公司一旦有一两个季度不及预期,就会被华尔街抛弃,结果适得其反。
第20章 社交网络和Facebook
1 通信的动物
2 社交网络1.0
3 Facebook
4 改变生活和大脑
……
但是,成功的社交网络都很好地利用了人的这样四个基本的需求,并且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服务:
其一,利用年轻人对异性的渴望;
其二,信息共享的需求,并且为了方便信息共享而提供部分账户共享功能;
其三,在线的脸谱和真实生活中的人之间的对应;
其四,建立某种意义上的朋友圈。
相反,花了很大努力却失败的社交产品,常常在上述某一个方面没有做好。至于能玩游戏、能进行支付,则属于锦上添花。
社交网络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生活和工作的习惯,这一点无需多言,我们都深有体会。过去我们梦想着智能手机出现后能够更好地利用碎片时间,但事实却是,我们只剩下碎片时间了,过去那种完整的能够深刻思考的时间不复存在。当这样的习惯持续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大脑也就随之改变。2010年,美国作家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 Carr)在后来被提名普利策奖的畅销书《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中介绍了美国医学院对互联网影响人类大脑发育和结构的一些成果。研究表明,长期倬用互联网后,负责浅层思考的脑沟变深了,意味着相应能力的增强;而负责深度思考的脑沟变浅了,意味着深度思考能力的丧失。当然,这些研究是在2007年左右完成的,当时社交网络的倬用频率远没有今天高,不过相应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中。到了2016年,特别针对社交网络对人脑的影响又有了一些新的研究结果,结论基本上和之前的研究相一致。研究表明,经常倬用社交网络的人,关注其他人的能力增加了,而阅读能力减弱了。易然教授们并不愿意用变好或变坏来总结这种变化,但是社交网络影响我们大脑的发育,进而影响我们的行为和做事方法是不争的事实,今天我们很容易受到社交网络上内容和情绪的影响,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
关于社交网络,还需要更正一个今天绝大部分人都会有的误解,那就是所谓的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 ’s Law),即网络价值和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这个定律是1980年提出来的,提出者梅特卡夫是当时计算机网络公司3Com的创始人。而当他提出这个定律的时候,计算机的网络规模只是几百台甚至更少的计算机,他没有见过几十亿人连接到一个网络上的情况。当网络中节点的数目巨量增加时,这个定律其实就不适用了,无论是对计算机还是对人都是如此。这就如同在低速环境中总结出来的牛顿力学定律,到了高速世界就不再适用一样。因此,梅特卡夫定律在如今用户规模上亿的社交网络上是不适用的,因为人能够维持的社会关系只有150人左右,这是由我们的基因决定的。一个社交网络即使再大,我们能够经常影响的人,和能够影响我们的人,通常还是只有几十人。今天你不论加了多少人的微信,通常也只会关注个位数的人的朋友圈,经常和几十个人通信而已。从各个网络公司实际的市值来讲,虽然Facebook的活跃用户是腾讯的三倍,但是二者的价值相差不大。推特公司的活跃用户数只有Snapchat的1/3不到,但是价值却更大,因为后者的用户过于低端。因此,社交网络的规模固然重要,但是它的用户质量以及提供的服务有效性更为重要。
结束语
1967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提出过一个“六度分离”理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五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五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这在当时只存在于理论上,因为无法大规模地验证。2016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做了两次试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个陌生人的照片,让大家帮助找出来,结果第一次在48小时内大家就找到了他确切的所在地,第二次花了不到24小时。也就是说,有了社交网络之后,全世界的每一个人真的就被这张无形的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第21章 成功的转基因 诺基亚、3M、GE公司
我们在介绍基因决定定律时说过,一家公司的基因往往决定了它的命运,而转基因对于大多数公司而言近乎不可能。即便是那些超级明星公司,包括Google和微软,稍微改变一下基因也是千难万难。比如Google就没有做通信公司的基因,因此它做不了社交网络的事情,而微软的基因是软件公司,做不好互联网的事情。但是,凡事总有例外,总有一些了不起的公司成功地从一个衰退的行业转到高速发展的新行业。这样,公司之间就有了伟大和平庸的差别。本章将介绍三个转基因成功的例子。
1 20世纪末的手机之王——诺基亚公司
诺基亚大事记
1865 诺基亚公司成立,但是主营业务是木材造纸。
1898 诺基亚前身之一的橡胶厂成立,与木工厂合并,诺基亚第一次成功转型。
1912 诺基亚前身之一的电缆厂成立,10年后并人诺基亚,第二次成功转型。
1962 诺基亚进人电子领域。
1970 诺基亚进人通信领域。
1982 诺基亚的合资公司推出汽车电话,很快诺基亚全资拥有了这家子公司。
1987 诺基亚推出移动电话(手机)。
1989 诺基亚推出GSM的移动电话,两年后开始提供GSM移动通信服务。
1998 诺基亚超过摩托罗拉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
2007 诺基亚占全球手机市场的40%,达到顶峰。
2008 诺基亚收购Symbian手机操作系统,它一度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2010 由于Android的崛起,Symbian的市场份额不断下滑,这一年第四季度,Symbian的市场占有率被Android超过。
2011 诺基亚决定放弃Symbian,转向微软的Windows Phone 7,但是市场占有率继续不断下滑。
2012 诺基亚因为业绩不佳,裁员一万人,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裁员。
2013 微软宣布以79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诺基亚的手机部门,并于2014年4月完成收购,2015年7月,微软宣布这项并购亏损76亿美元。
2019 微软宣布放弃它的手机操作系统。
2 道琼斯指数中的常青树——3M公司
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股票指数道琼斯,只覆盖了30家公司。但这30家公司是美国经济中最具代表性、长期发展稳定并目关乎到美国经济命脉的大公司。道琼斯不断淘汰过时的公司,然后吸收新鲜血液,思科、英特尔和微软就是近十几年来被加人进去的。而许多曾经辉煌的公司,比如美国钢铁和合并前的AT&T就被剔除了。由于美国和世界产业的变迁,能几十年一直留在道琼斯指数中的公司寥寥无几,3M公司便是这些凤毛麟角中的一个。到2018年,3M在全球有93000多名雇员,实现产值320亿美元,纯利润54亿美元。
每个人了解3M的途径各不相同。很多人通过思高(Scotch)胶带了解3M公司,而早期的PC用户是因为它的软盘,家庭主妇们可能是通过它的洗碗布知道3M的,而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各种从业者可能知道它是今天世界最大的液晶生产厂商之一。另外还有很多搞工程的人也直接或间接地与3M打过交道。没有人能完全说清楚3M公司是做什么的。有些读者可能会奇怪这个产品种类五花八门的公司和《浪潮之巅》有什么关系。本书介绍3M公司是因为它是全球公认的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也是少数能在产业不断变迁的世界经济发展中不断成长的常青树。
3M公司过去的全称为明尼苏达矿业和制造公司(Minnesota Mining andManufacturing Company),首字母缩写是三个M,人们习惯地称它3M。到后来3M众所周知,而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最初的名字了,所以从2002年起,它干脆改名为3M公司。
3M公司于1902年诞生于明尼苏达的苏必利尔湖畔,最初是从事采矿业的,大家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为了和同行竞争,3M公司的老板鼓励工人们发明创造新产品,并成立了研发部门,而那些新产品不断取代现有产品,成为公司新的核心业务,倬得公司不断成功转型。3M公司至今最富传奇的故事就是思高胶带的发明。
发明胶带的是3M的一个小人物一—理查德·德鲁(Richard Gurley Drew)。1923年的一天,技术员德鲁到一家汽车喷漆厂去办事。当时美国流行双色汽车,但是喷漆很麻烦。当时的工艺很落后,汽车厂的工人先在车上喷上一种漆,然后用胶将旧报纸糊到车上,挡住不需要喷漆的地方,再喷上第二种漆。用胶水糊报纸的方法很难控制质量,胶涂少了粘不住报纸,第二种漆喷不整齐;胶水用多了,不仅擦不干净,还会破坏车身的美观。德鲁无意间听到工人们的抱怨,有心发明一种既能牢牢贴在两种颜色接头处,又很容易撕掉的胶带。
德鲁回公司后私下里就研究起胶带来了,老板看到他“不务正业”也没说什么,由着他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很快,德鲁就发明了一种不干胶带,取名为Scotch,原意是恶搞他的苏格兰(Scotland)老板,想不到这种胶带和它的名字从此在全世界流行。以后,胶带成了3M公司的主要业务,并目研制出各种各样适用于不同场合的胶带。不要小看了这些小小的胶带,它的市场直到2000年以前,比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市场还大,而3M一度占据全球四成胶带市场。不仅如此,胶带的学问也很多。3M的胶带家族有光学透明双面胶带、光学透明胶、导电胶带、导热胶带、绝缘胶带、屏蔽胶带、高温胶带、热熔胶带、遮光胶带、黑白双面胶带和警示胶带等上百种,其中有一些我们既说不上名字又想象不到其用途。我自己就有过一次和特殊胶带打交道的奇遇。那次我乘坐的飞机从芝加哥到西雅图,登机后等了很久还不起飞。机长告诉大家,机翼上有一扇砖块大小的门关不上。当时正值午夜,找不到机械师能在短时间内修好,所有的乘客都很着急。最后,航空公司决定用一种“高速胶带”粘住这扇关不严的门,然后把我们送上了天。一路上,我提心吊胆,不时通过飞机的舷窗看着那块由胶带打的补丁,生怕它被风吹下来。令人欣慰的是,飞机以每小时900公里的速度飞行了三个多小时,那块胶带居然没有被强风吹开。从那时起,我才渐渐懂得小小的胶带里大有学问。
截至2011年,3M公司发明了6万多种大大小小的产品虽然3M公司随后没有更新近年来发明的总数,但是该公司的创新力一直延续至今,在2015年,它获得了第10万个专利。今天,全世界有一半的人每天直接或间接地接触3M的产品。该公司营业额中有1/3来自于近5年的发明,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员工利用工作时间从事非工作性质的研究搞出来的。3M允许员工用15%的时间干任何自己喜欢做的事,后来这种做法被Google学去了,变成了Google的“20%项目”。2008年,在最具有创新力的公司里,3M的排名竟超过Google和苹果这些以创新而闻名的公司。创新力是3M公司近百年来长盛不衰,并且成功地从矿业公司转变为电子和日用品公司的根本原因。由于公司的每个员工头脑里总是有创新这根弦,3M公司总是能随着时间、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的变革搞出一些有用的小发明。而这些看上去不大的发明却能开拓出一个不小的市场。
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个人计算机的普及,软盘用量大增,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峰期,全球软盘的市场规模达30亿—40亿美元。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倬用计算机的读者一定还记得3M的软盘,它被公认为是最好的软盘,当然价格也是最贵的。我自己了解3M便是从3M软盘开始的。3M一直占领全球1/6的软盘市场,市场份额在所有软盘厂家中最高。软盘是IBM发明的,IBM之后世界各地出现了不下上百家软盘厂家,因为软盘算不上什么太高科技的产品。3M之所以后发制人,成为这个行业老大,除了它的产品质量一直稳定外,主要是靠一项发明专利—一软盘中特殊的防霉套。拆解过软盘的读者知道,打开软盘的塑料外壳后,可以看到在磁碟和外壳之间有一层白色的布状保护膜,那就是软盘的防霉套,作用是防止软盘长霉菌,同时保证磁碟在转动时不会被塑料外壳划坏。几乎所有的软盘生产厂家都知道软盘中磁碟是核心,它的质量最重要,因此像样品牌的软盘磁碟本身都没有问题。而这小小的防霉套的质量就千差万别了,一些廉价的软盘厂商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很便宜的纸套子,这些软盘在磁碟还有很长寿命时就被劣质外套划坏了。3M靠这么一项小发明,便产生了每年几亿美元的营业额。当然,在个人计算机蓬勃发展时,3M成立了很大的存储设备部门,除了软盘外,还生产磁带、光盘和读写设备。
当然,IT行业更新很快,一个市场可能存在不了几年,同时又不断会有新的市场出现。大部分公司会随着一个产品市场的衰退而消失。比如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广泛使用了20年的计算机软盘、用了30年的录像带和录音带,以及有上百年历史的摄影胶卷。很多专门经营这些产品的公司包括著名的柯达公司,或者已经关门,或者已黄鹤杳然下。一家公司必须不断推出新产品,才能替补老产品不断萎缩的市场。同时,新的市场又催生新的公司。3M总是有无数的发明作为技术储备,当新的市场兴起时,它都能搭上新兴市场的快车。我们在前面的基因决定定律中讲到,在一个大公司内部,现有部门的主管因为给公司带来了利润会有很大的发言权,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阻挠新产品部门的发展。为了顺利转型,公司在开发新产品的同时,必须痛下决心把旧的产品部门分离出去。因此,当软盘、磁带和其他计算机存储设备成为发展慢、利润低的产品时,3M会果断地将这些部门分离出去单独上市,比如现在的Imation公司。
在软盘和计算机存储设备之后,3M成长最快的产品是液晶显示器产品。当然,液晶产品和存储设备是两回事,液晶产品的发明并不是由开发计算机软盘的工程师利用15%的时间做的,而是由3M原有的材料和化学部门的一些科学家工程师完成的。
液晶是一种同时拥有固态晶体和液体双重特性的物质,“液晶”二字得名于此,它可以流动,又有晶体的光学性质。液晶对电磁场很敏感,在电磁场作用下,它的分子排列会发生变化,这样就可以通过控制光的偏振方向来决定光的亮度,并目根据这个原理制成显示薄膜。液晶材料在100多年前就由奥地利科学家发明,但是80多年后才被日本精工爱普生公司用于制作显示设备。3M不是液晶显示薄膜的发明者,甚至不是它早期的生产厂商,但是3M却后来居上,成为当今世界上主要的液晶显示薄膜生产厂商。2006年以来它40%的年收人和1/3的年利润来自于液晶产品。而这一业绩也是靠一项关键性的发明一—增光膜(Brightness Enhancement Film,BEF)获得的。
液晶薄膜作为显示器,最大的问题是亮度不足,而3M公司的增光膜技术可以将液晶薄膜的透光率提高一倍,因此采用3M公司LCD生产的显示器和电视机亮度高,色彩鲜艳,而目省电。此后,3M又发明了十几种和LCD有关的产品,在LCD市场占有很高份额。从2007年起,3M公司的LCD年销售额超过100亿美元。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3M的主营业务除了传统的个人消费品和医疗用品外,重点集中在电子和能源产品(电子产品和能源产品的材料和元器件)、工业品(比如过滤器、净化器等),以及安全和图形显示产品上(显示设备和各种安防设备)。到2014年其营业额连续7年增长,其股价几乎翻了一番,而同期道琼斯指数只增长了37%左右(图21.2)。
图21.2 3M股价(上)和道琼斯指数(下)对比
一家公司成功一段时间不难,难的是能百年来长盛不衰。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3M是少数业绩几乎没受到影响的跨国公司,足以说明它的稳健。今天,3M的创新依然在继续,这些创新倬得它在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机电产品等诸多领域都领先于世界。比如它发明了最新的纳米材料,用这种材料制成的自行车车架,只有667克(半千克多一点);它的新型太阳能薄膜,光电转换效率非常高而成本却很低,可以为非洲等基础设施落后的地区解决照明问题。3M作为一棵百年常青树,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大家借鉴。3M也是商学院教程中研究得最多的公司之一。我个人认为它能不断转型的原因最关键的有三条:两条容易看到的,和一条不易察觉到的。
第一条经验大多数学习管理的人都清楚,就是坚持以创新为公司的灵魂。3M公司一直强调要有1/3的营业额必须来自近几年的创新,这样它才能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立于不败之地。为了鼓励创新,公司不仅留给员工15%的工作时间用于创新,而且对于员工的工作安排和计划弹性非常大,这样才能让员工放手去干。3M公司甚至希望各级主管容忍和宽容下属提出的但自己并不赞同的项目,以免扼杀可能成功的发明。主管对员工放手的管理方式,使得3M的发明创造多种多样,很多看似毫无关联。因此有人称之为“离散式的发明创造”。对3M来讲,发明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明本身。
第二条也不难看到,却不容易做到。3M公司会适时强制淘汰一些看似还在赚钱但是前景不是很好的产品。当计算机存储设备和产品还能赚钱时,3M公司果断卖掉了该业务。在很多经营者眼里,开拓新的业务没必要放弃旧的业务,何况旧的业务还在赚钱。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基因决定定律中指出的,旧的业务部门一直在为公司赚钱,因此这些部门的主管在公司里发言权很大,很可能为了部门利益,妨碍公司转型。有长远发展眼光的公司一定会将发展前景不是很美妙但还值钱的部门卖掉。
第三条是很多人忽视的,就是3M的发明和产品都是针对广大用户的,而目是消费类的。相比面向企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营业额相对稳定,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当一家公司转型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邯郸学步。旧的行业江河日下,收人在减少,而在新的行业则要从头开始,失去了原有的优势,短时间挣不到利润。这样,整家公司效益下滑,很容易被华尔街投资者看衰。但3M公司因为产品数量多,其中大多数产品销量和利润稳定,为3M提供了足够的财力,保证它的新产品上市并占领市场。很多公司,尤其是专营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公司,很难做到这一点。除了像IBM那样为企业提供IT服务的公司,通常企业级产品和服务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太大,收人相对不如消费产品来得稳定。
这三条经验保证了3M公司百年来不断创新,长盛不衰。这些经验早已写入教科书,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公司并不多,这才显示出3M的不凡之处。
3M 公司大事记
1902——3M公司成立,主营采矿机械。
1921——发明防水砂纸,并且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
1925——德鲁发明胶带,至今仍是3M主要产品之一。
1945——1945年后,3M工厂扩展到全美国。
1950——1950年后,3M成为全球性公司。
1969——发明自动可编程交通红绿灯系统,被广泛使用,直到2007年停产。
1970——1970—1980年,进入录音录像设备市场及数字存储市场,直到1996年将这部分业务单独上市。
1993——3M光学部门发明液晶增光膜,至今仍被广泛使用。其后,3M发明了几十种液晶和等离子体产品。
2007——3M进人可再生能源市场。
3 曾经的最大企业联合体
了解GE公司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家充满传奇色彩的公司是由著名发明家爱迪生创立的,是将电最早介绍和普及到世界上的公司。它现在的英文名字是General Electric,简称GE,100多年前它进入中国时,根据字面意思及其经营的产品,GE被翻译成通用电气公司。也许是因为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故事家喻户晓,今天GE在大部分人印象中仍然是生产电灯、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的公司。但实际上,GE早就跟“电气”没有多大关系了,如果还按通用电气的字面意思来理解今天的GE公司,显得有些以偏概全。GE这类公司在企业界有一个专有名词Conglomerate,即联合体的意思,除了GE外,算得上是联合体的公司还包括韩国的三星公司、巴菲特控股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等。不过,在所有联合体中,只有GE能够在一个多世纪里长生不衰,因此它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联合体。到2007年年底,GE的规模和营业额达到了巅峰,它包括6大部门,每个部门独立来看,在各自的领域都是佼佼者。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GE巅峰时期,这6个部门按2007年的纯利润排序如下:
- 全球基建架构部门(Global Infrastructure),108亿美元;
- GE(企业)金融(GE Finance),60亿美元;
- GE(个人)金融(GE Money),43亿美元;
- 电视新闻网NBC和环球电影公司(Universal),31亿美元;
- 医疗保健部门(Health Care),31亿美元;
- 工业部门(Industrial),17亿美元。
其中只有利润最少的工业部门的一个子部门电器(appliance)是唯一和GE名称直接相关,利润倒数第二的医疗保健部门因为制造医疗仪器,和通用电气的名称勉强能拉上些关系,其余跟电气已毫无关系。今天,虽然GE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影响力不如从前,但它依然是全球发展最稳健、也是最快速的大公司。那么GE是怎么从一个电气公司发展成全球巨无霸的联合体的呢?让我们先回顾一下GE的发展史。
3.1 百年扩张,从有线电到无线电
美国著名发明家爱迪生发明电灯以后,于1890年创立了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Edison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该公司不仅生产电灯泡,而且经营从发电到铺设电线,再到安装电灯的一条龙服务。当时的民众不认同电的好处,对电普遍存在畏惧心理,经常破坏电路。为了普及电的应用,爱迪生不得不派人在电线经过的地方巡逻。经过爱迪生的努力,电得以在美国首先普及。因此,GE对于美国整体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功不可没。1892年,在金融家J. P.摩根的帮助下,爱迪生通用电气和另外两家公司合并,改名为通用电气。1896年,道琼斯指数出现,GE是道琼斯指数最早包含的12家公司之一(1914年道琼斯指数成分股发展到20家,1928年发展到现在的30家),其他11家大部分或已破产或被收购,剩下的规模已经萎缩得非常小了
本来最早起步的GE在发电和电力供应等工业领域并没什么对手,但是由于爱迪生后期在直流输电和交流输电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他错误地坚持直流输电比交流输电好,结果让首先进行交流输电的西屋电气公司占领了很大的市场(交流输电容易变压,在输电过程中能量损耗小)。失去电力供应市场统治地位的GE开始拓展新的业务。这种扩张100多年以来从不间断,一直持续到今天。
GE的第一次扩张是从有线(动力)电到无线电收音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被打得千疮百孔。美国军方(海军)发现无线电很有用,便鼓励GE买下了无线电发明人马可尼(意大利人)的无线电公司,GE把它变成了一个独立上市的子公司RCA(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美国无线电公司)。我们从GE经营广播可以看到它今天经营电视网和影视公司的影子。同时,我们可以看到GE的经营模式,即保持子公司的相对独立。
RCA在20世纪美国历史上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公司,与GE一道制定了我们今天采用的很多标准,比如各种电缆、信号线、电源插座的接口、收音机和音箱喇叭的电压电阻标准,等等。更重要的是,它的RCA实验室一度与贝尔实验室齐名,有很多大发明,包括很多种电子管、早期的一些雷达和真正实用的电视显像管(CRT)、最早的彩电(但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方形的,而是圆形屏幕的),等等。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RCA几乎是全世界唯一能生产彩电所有部件的公司。
说到RCA的彩电,它还牵扯到一件中国文革时期有名的政治事件一一蜗牛事件。文革后期的1972年,中国开始考虑上彩电项目。国务院派人到世界各地考察,发现日本需要好几家公司才能把彩电显像管的玻璃壳、荧光粉等部件凑齐,但是到了美国,RCA一家就能全部搞定。在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中国和RCA达成了引进彩电显像管生产线的协议。谁知天真的美国人(RCA玻璃供应商康宁公司的人)为了表示友好,送给了中国代表团一些漂亮的玻璃蜗牛纪念品。后来被“四人帮”说这是讽刺中国为“蜗牛”,并以此攻击周恩来总理,制造了“蜗牛事件”,引进彩电生产线一事也就泡汤了。这件事对中国影响非常大,后来从第三方引进彩电生产线多花了一倍的价钱不算,还让全中国的人晚了好几年才看上彩电。最糟糕的是,中国从此放弃了美国的NTSC彩电制式,采用了欧洲的PAL制,以至于计算机显示器和彩电的制式不兼容。现在,中国不得不每年多花很多钱来生产全制式的彩电。讲了这么长的故事,只是为了说明GE的RCA曾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公司。
自从有了RCA,GE就有了发电(供电)和家用电器两大业务,它们分别是今天GE全球架构和GE工业两个部门的雏形。GE的发电从传统的火力发电扩展到建立核电站,继而又扩展到和整个能源和工业工程相关的行业,包括海上钻井采油,建立大型的工业设备和工程。而GE的家电部门,不仅发展成品类齐全的各种电器,包括洗衣机、电冰箱、微波炉、电视机等,而目扩展到飞机发动机等工业设备。今天,GE是全球飞机发动机的主要生产商,它的发动机用于波音747/767、空中客车很多系列,以及美国第四代主力战斗机F35。在这个大部门里,家电的地位越来越不重要,因此,这个部门的名称都改成了GE工业。
由于收音机和无线广播需要制作节目,因此GE、RCA和老对手西屋电气于1926年共同创办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很快,GE的RCA和NBC就控制了整个美国的无线电广播市场。虽然在反垄断的约束下,NBC不得不分出一半成立了一家新的广播公司—一美国广播公司ABC(现在是迪士尼的子公司),但它至今依然是美国最大的广播电视网。通过NBC,GE不仅赚足了电视广告的钱,而目在娱乐业占了一席之地,后来又收购了环球电影公司,进人了电影行业。
GE的这几次扩张都比较成功。主要原因有两点,首先这些扩张都是在已有业务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展开的,整个转变过程比较自然。其次,GE进人的都是一些全新的或刚刚起步的领域。在20世纪初,无线电收音机还属于高科技领域,而广播市场也才刚刚起步。二战后,电视机尤其是彩电则是当时的高科技产品,而电视网络在美国的发展也是方兴未艾。GE很少进人一个已经成熟而且竞争对手很多的市场。作为全球最大的公司,GE的创新已经不能仅仅是一两个产品的创新,而必须每次创出一个新的行业。从发电和电灯,到无线电和收音机,再到电视网和彩电,每一次GE都创出了一个新的行业。
当然,GE的扩张也有不少失败的,但是它能很聪明地及时将不可能成功的业务终止掉,不至于陷得太深。GE“著名”的失败例子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人计算机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很多公司都力争在新兴的计算机工业中占有一席之地。GE靠着RCA强大的研究中心,也挤进了计算机领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计算机工业界的格局是一大七小,大的是IBM,GE是七个小的之一。在计算机界,人们将这一大七小戏称为白雪公主(IBM)和七个小矮人。GE当然不愿意做小矮人,上个世纪80年代它看到和IBM竞争无望,便将计算机部门卖给了霍尼韦尔公司(20世纪80年代在清华和北大计算中心用过计算机的读者应该用过霍尼韦尔的计算机)。
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一项新的医疗成像技术核磁共振(MRI)在临床诊断上显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GE便抢先投人巨资开发核磁共振机,并目在这方面获得了成功。GE后来又收购了一家技术领先的核磁共振公司,加强了它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大医院放射科的专家都知道,GE的核磁共振机才是真正高端的设备,而西门子和安捷伦(原来的惠普)相比就要低一个档次,而日本品牌可能又要再低一个档次。如今GE的医疗仪器部门已经发展成它的六大部门之一。
3.2 从实体经济到金融
GE最近的扩张是进人银行和金融领域。在金融风暴前,银行和金融部门对GE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其他部门。银行和金融业务看上去和GE原有的实体工业无关,GE此前在金融业也没有什么经验,这样的扩张一般来说是非常忌讳的。但是,GE这种非常规的扩张在它的特殊情况下却是合理而有根据的。
图21.3 GE Monogram品牌被看成是品质的象征
GE的家电产品大多数是同类产品中高端的,比如在档次上,GE的Monogram系列冰箱仅仅比奢侈品牌Sub-Zero低一点点(图21.3)。它价格昂贵,是同样大小的日本和韩国高端冰箱的两倍以上。即倬是它的Profile系列电冰箱也是中高档产品。这么贵的冰箱,很多家庭需要分期付款才能购买。因此,GE为了促销就借钱给信誉好的家庭,而借贷的利率常常高达15%到20%左右,可以算是高利贷了。而美国很多家庭只要每月付得出月供,常常不去仔细算利息,这就让GE赚走了很多钱。这样一个冰箱卖下来,GE从贷款中得到的利润比冰箱本身的利润还要高。GE发现这种办法很好,就向美国政府要求开一家银行,就是现在GE的商业银行(GE Money Bank)。GE和美国政府的关系很好(以后还会讲到),因此,美国政府就同意了(后来,世界最大的百货店沃尔玛和世界最大的建材店家得宝也想这么做,美国政府就没有同意,当然这是题外话了)。有了自己的银行,GE可以用来提供贷款的现金就一下子多了起来,它便与电路城公司(即Circuit City,2008年底申请破产)和百思买等商量,为这些电器商店出售的所有大件商品提供贷款。这些电器商店一看这样既可以提高销售额,又不用承担风险,于是就都答应了。这样,GE就发行了电路城、百思买等联名信用卡。由于GE做事谨慎,不胡乱贷款,贷出去的钱(在2008年金融风暴以前)很少遇到赖账的。随着GE金融业务的发展,它将信用卡业务扩展到了各种各样的商家,包括品牌服装店Gap、安·泰勒(Ann Taylor)等,杰西潘尼百货店(JC Penney),高端家具店伊森·艾伦(Ethan Allen)和汤美思(Thomasville)等。到现在,在美国除了万事达、维萨、运通和发现(Discover)四种通用的信用卡,其他各个连锁店发行的五花八门的信用卡背后的银行只有一个,便是GE。同样的道理,GE在全球承接各种工程时,对于一下子拿不出全部合同费用的大公司和政府,它也会提供商业贷款,这便产生了GE的商业贷款部门。到2007年,GE的金融和银行业务带来的利润已经占到GE利润的四成。
当然,随着GE不断开拓出新的业务,它也必须将过时的业务淘汰掉。长期以来,GE不断卖掉那些效益不好或前景不看好的部门。2000年以来它先后卖掉了塑料、高端材料、财产和风险保险、再保险及欧洲的医疗保险等部门,收回了上百亿美元的现金。这些部门有些在亏损,有些易仍盈利,但是GE不看好它们的前景(比如塑料部门),便在它们还值钱的时候出手卖掉。
GE从家电和其他实体经济进人金融领域的过程看上去很自然,至今也很成功。但是为什么其他公司不能模仿呢?事实上,很多公司都试图模仿,但是都不成功,GE是至今唯一开办银行的大型实体公司。这里面原因有很多。首先,实体公司办银行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和支持。在美国办银行本不是一件难事,任何有良好信用记录的人只要有几百万美元的抵押金就可以申请开办银行,这也是美国有8000多家大大小小银行的原因。但是,对于大实体公司,尤其是大到主导了一个行业的公司(比如沃尔玛),美国政府反而对它们办银行非常小心。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造成垄断,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产生不良的金融资本影响经济。GE和政府的关系很好,它在某种程度上支撑着美国的基础建设、航空工业和国防工业,这些远不是沃尔玛和家得宝公司可比的。相比之下,沃尔玛易然是美国最大的私营雇主和全球最大的连锁店,但是由于为富不仁,在民众和政府眼里形象都很差,办银行这件大事很难获得广泛支持。而家得宝公司虽然热衷于公益和慈善事业,但是毕竟财力不足,也无法提供大量商业信贷。
GE能够办银行的第二个原因是它的信用记录和还贷能力非常好,让所有人放心。到2007年底金融危机前,GE一直是美国(可能也是全球)仅有的五家信用评级为AAA的公司。其中有三家是债券保险公司,金融危机一开始这三家就因为给次贷担保损失巨大,已经无法维持AAA的评级了,另外一家是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AAA信用是什么概念呢?这是美国州政府信用的最高级和美国、英国两国国债的评级。美国最大的几家商业银行,包括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等,即使在金融危机前信用评价也不过是A+到AA,金融危机后一度被降级成BAA。而中国的几大国有银行的评级长期在BAA左右,后来才达到A。GE的信用是它上百年积累的结果,而一家历史很短的公司(包括思科和Google这样有几百亿现金而无债务的公司)很难有这样好的信贷评级。虽然GE和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信用在2009年3月被降级成AA+,导致金融危机前世界上全部五家AAA的公司都未能维持这个评级,不过GE的信用度仍好过美国大部分州政府和欧盟大部分国家政府的信用度,比如加州政府的信用度只有A+。(微软、思科和Google公司在金融危机后加人了评级,分别被评为AAA、AA和AA。因此,微软是直到2012年世界上唯一一家评级在AAA的公司。)信用记录好的最大用途在于贷款的成本比竞争对手可以低很多。评级AA的公司贷款的利率可能只有BAA公司的一半。
GE从事金融业务是一把双刃剑,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它无疑将提升GE的实体业务,但是在遇到金融危机客户还不出钱时,那些借出去的钱便都变成了坏账,不仅在金融业务上产生亏空,而目拖累了它的实体业务。因此,在金融危机之后,GE缩减了金融部门,并采取更稳健的投资策略。
3.3 领袖的重要性
即倬不断在淘汰旧的、过时的部门,GE的部门相比任何一家公司还是多多了,把这样一个联合体整合好,难度非常大。郭士纳把庞大的IBM帝国比喻成大象,而GE的业务种类比IBM又多了很多,把它比作恐龙恐怕也不为过。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说到了,很多公司扩张到一定规模时,管理就开始失控,最后丢掉了核心业务,并目开始江河日下了,有些甚至被华尔街拆了卖掉。GE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要归功于它在全球所有公司中数一数二的管理水平。
GE历来出“将相之才”,它的一个部门主管到了很多公司都能独当一面,它的CEO则更是难得的管理奇才。在GE历代CEO中,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最为突出,我想用“国士无双”来形容韦尔奇也不为过。韦尔奇从1981年开始执掌GE,到2000年退休。在这20年中,近1000次的企业并购和部门拆分,把GE从全球排行十几名的公司,发展成全球最盈利、市值最高的公司。1981年,GE的营业额为250亿美元,2000年达到1300亿美元,纯利润超过100亿美元。GE的市值从1981年的140亿美元到2000年夏天达到5000亿美元,并维持到当年的年底在韦尔奇担任CEO的20年里,GE每年给股东带来的投资回报超过20%,接近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水平。到韦尔奇退休时,GE一共有9个单独的部门,如果作为独立的公司,每个都有资格入选财富500强。
和很多跨国公司空降的CEO不同,韦尔奇是在GE土生土长的,他全部的职业生涯都在GE度过。1960年,25岁的韦尔奇从伊利诺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就进人GE从事技术工作。11年后,他成为GE最年轻的部门总经理,又过了10年,他成为GE历史上最年轻的CEO,那一年他刚过45岁。在GE工作了20年后,韦尔奇对GE这个百年老店的优势和问题看得一清二楚。和很多历史悠久的跨国公司一样,GE在管理上官僚作风严重,在业务上保守,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GE没有什么发展,人数却年年增加。到20世纪80年代初,GE的员工数达41万之多,但是它只在传统的供电、发动机和照明领域还保持着原有的优势,其他部门则业绩平平。
韦尔奇上任后和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口号相同,就是变革(很巧的是,奥巴马担任总统时的年龄和韦尔奇当年差不多,但是他可没有韦尔奇幸运)。首先,在人事上,他裁减了一半高管,同时裁掉了10%表现最差的经理。GE以前级别森严,上下级沟通渠道不畅,韦尔奇为了改变这种风气,有时很不“职业”地越级了解情况或传递自己的想法。韦尔奇后来在回忆录中认为,他这种不守规矩的做法是他给GE带来的最大价值。像GE这样“传统”的公司,以前除了高管们,普通员工是没有股票期权的,韦尔奇改变了这个规矩,将期权的范围扩大到1/3的员工。在接下来的5年里,韦尔奇裁掉了8万名雇员,并目通过出售一些部门又减少了3万名雇员。到1985年,GE只剩下30万人,而韦尔奇同时也得到了“中子弹杰克”的恶名。
在GE的业务发展方向上,韦尔奇做了重大的调整,他大刀阔斧地出售了很多部门,并开展大量的并购。其中最著名的并购是通过将RCA私有化而收购美国最大的广播电视网NBC。我们在前面讲到,RCA是GE的一个子公司,但是后来按照政府反垄断的要求,成为一个单独的上市公司,很多股票在其他股东手里,RCA同时拥有NBC的一大部分股份。1986年,GE回收了RCA手里的全部股份,从而将NBC变成全资子公司,并且在电视和娱乐业占领了制高点。RCA除了NBC的电视网外,还有很大的电视机等家电业务,但是韦尔奇根本不看好它那曾经辉煌的家电业务,转手卖给了法国的汤普森(Tompson)公司,同时换来了汤普森的医疗仪器业务。在这两次重组中,GE甩掉了低利润、竞争激烈的彩电业务,获得了两个高利润而目有前景的电视网和医疗仪器业务。这两个部门现在都是GE的支柱部门,而并购了RCA家电业务的汤普森果然每况愈下,后来不得不将该业务卖给中国的TCL公司。
在GE的CEO生涯中,韦尔奇的另一个大手笔就是大力推动金融资本与制造业相结合,将原来GE很小的消费产品贷款部门,扩展成GE的商业银行(GE Money Bank)和提供制造业的贷款、保险和金融咨询业务的GE金融部门。同时韦尔奇通过合作和收购,在不到十年里,将GE的金融业务扩展到全世界。今天,GE商业银行在全球五十几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今天的GE基本上保留了韦尔奇留下的布局,经过业务重组,GE成为最具有活力的公司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韦尔奇是让恐龙跳舞的人。
韦尔奇不仅留给了GE一笔丰厚的财富,包括在全球庞大的资产、价值几百亿美元的GE品牌(2011年GE的品牌价值为428亿美元)和管理之道,而且培养出众多工业界领袖。GE的每个部门都堪比一家财富500强的公司,并且很多部门之间并没有太大的联系,比如GE工业部门和它的NBC就没有什么关联,因此,GE为每个部门设立了一个独立的CEO(相当于政府的省长)。韦尔奇从这些人里面提拔和培养接班人,其中最著名的是三个候选接班人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吉姆·麦克纳尼(Jim McNerney)和鲍勃·纳德利(Bob Nardelli)。韦尔奇在任的最后几年里,非常注意培养和考验他们三个人。但是,GE只能有一个CEO,最终伊梅尔特在竞争中胜出了。麦克纳尼随后去了3M公司担任CEO,几年后他担任了波音公司的CEO,扭转了波音对空中客车的颓势。另一位候选人纳德利离开GE后担任了美国最大的建材公司家得宝的CEO,五年里将家得宝的营业额和利润翻了一番,但是因为他没有能提升家得宝的股价,被赶出了公司,后来纳德利是克莱斯勒公司的CEO,直到2009年该公司被卖给意大利的菲亚特公司。伊梅尔特经营GE的策略用中国的老话讲就是“萧规曹随”。他完全沿袭了韦尔奇的经营策略。也许是自觉没有韦尔奇那样统帅超级大公司的能力,伊梅尔特进一步合并GE的部门,现在便剩下了前面提到的6大部门。
韦尔奇退休后,他的一举一动仍然引人注目,他多次前往中国和国内的企业家聚会。同时,他成立了一个培养高管的杰克·韦尔奇管理学院(Jack Welch Management Institute),给各个公司的高管进行培训。他写的《杰克·韦尔奇自传》和《赢》两本书均成为全球畅销图书。这两本书的中文版从各大图书城到地铁和路边的小书摊都有出售。
有人认为韦尔奇不过是运气好,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美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了六七年,而同时上台的韦尔奇不过是沾了里根的光。到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苏联和东欧解体及中国的开放,带来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GE又沾了光。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如果GE在20世纪80年代没有韦尔奇,它很可能像AT&T那样,让华尔街拆了卖掉,而华尔街会美其名曰单独上市。好一些的情况是,GE像德国西门子或荷兰飞利浦那样,易然没有解体,但也发展不大。因此,没有韦尔奇就没有GE的今天。韦尔奇接手时,GE有很多的资产却不能盈利。这种公司,最容易被投资者(或叫投机者)拆了卖,因为它有很多固定资产,只要将它亏损的业务全关闭后,便能卖出好价钱(而微软和Google这种固定资产不多的公司,拆了卖不出什么好价钱,投机者不感兴趣)。实际上,华尔街一直在研究将GE的工业部门卖掉的可能。韦尔奇不是AT&T那些短视的股东,他要建立一个全球最大的经济联合体。他知道与其让华尔街对GE动刀子,不如自己做手术。像GE这么大的公司,不是一两个大发明就可以让它转基因、转型的,它要想成功转型,必须发现并培养出一个新的行业。因此,韦尔奇不断地淘汰前景不好的商业部门,融人新兴的产业部门,经过20年时间,终于成功地将GE从传统的工业公司打造成集高科技、高附加值服务、金融和娱乐于一体的航空母舰。
3.4 艰难的自我更新
后韦尔奇时代的GE,每年仍在持续高速发展,而目发展速度是美国GDP增长速度的三倍。从2003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GE仍保持每年14%的营业额增长和16%的盈利增长,这在大公司中很少见(见图21.4)。
图21.4 金融危机之前GE的营业额统计
作为一家年收入近1500亿美元的巨型公司,GE已经无法维持韦尔奇时代的发展速度了,它的市值多年都没有得到太大的提升。2008—2009年,拥有一家商业银行的GE也无法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到2009年3月,GE的市值已经比一年半前缩水了80%。但是,由于GE有很好的管理经营和健全的体制,并且各个领域都在同行业中有最强的竞争力,即使今天为它带来一些问题的GE金融部门,在整个金融领域中也是问题最少的。因此,包括巴菲特在内的长线投资家仍然看好GE,并大量注资GE。到2010年,GE各个部门全部恢复到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有些业务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同时股价回到峰值的一半。
在从2010年开始接下来的5年里,GE进人了新的一次转基因。在一般人印象中,这些巨无霸公司转身很难、很慢,事实也确实如此,不过GE还是下了决心转型。在2008一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GE对自身业务做了重大的调整。我们在前面提到金融危机前GE有六大部门,即基础建设、商业金融、个人金融、保健、影视新闻(NBC Universal)和工业部门,在金融危机之后GE的产业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GE在2013年卖掉了依然盈利但是也不断受到互联网新媒体挑战的影视新闻业务,其次它将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两个独立的金融业务合并,成立了新的金融部门GE Capital。为了适应当下和今后20年全球新的经济发展趋势,主要是全球对环境的重视、对能源的重视,以及美国可能将要开展的对基础设施的全面升级,新技术革命可能带来的对全球企业级IT服务的颠覆,GE对未来的产业做了重新布局,成立了与新能源以及环保有关的能源和水资源部门(GE Power & Water,包括风能发电)、针对页岩油气开发的石油和天然气部门(GE Oil & Gas),以及与基础设施建设及交通有关的GE交通部门(GE Transportation),同时它将原来的工业部门一分为二,变成以生产发动机为主的航空部门(GE Aviation)以及生产传统家电、新型家电和企业级设备的家庭和商业解决方案部门(GE Home & Business Solution),当然保健部门原封不动保留了下来。在随后的两年里,GE仍在不断优化部门结构,并且出售了家电业务,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像GE这样的大公司,进行如此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第一个代价就是营业额和利润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按照GE预先的设想,在调整和转型完成之后,产业结构更能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求,业绩会在很长时间里不断提升,但是这个难度显然超出了它当初的估计,因此从2016年开始,GE陷入了三十年来的低谷。易然GE这些年来一直维持着千亿美元的销售额,但是利润率不断下降。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企业,特别是和制造业相关的企业整体竞争力在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GE一直未能走出转型期。华尔街对GE的耐心在2016年已经丧失殆尽,因此从那时起,它的股价一路下跌。2018年中,GE由于利润下降,股价下跌,终于被道琼斯指数除名了,至此道琼斯最初的所有成分股公司都被踢出这个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工业企业股票指数。
不过,如果说GE已经是昔日黄花为时尚早。它的一些业务是关乎到国计民生的,在很长时间里不仅不会消失,而目还在发展,比如和能源相关的很多业务,包括核电站、发电机、高压电技术、油气田设备、风力发电设备,以及为能源部门提供咨询服务,这些业务都不会像IT行业的很多产业那样迅速消失。在GE所有的业务中,最有竞争力的当属航空发动机了。GE是世界上仅有的三家大型民用喷气式飞机发动机制造商(另两家是美国的普惠和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此外,它在医疗仪器行业以及各种大型复杂动力设备领域,依然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企业之一。
公平地讲,GE目前转型的思路是清晰的,那就是回归制造业。只要对比一下今天GE的八大部门和金融危机前的六大部门,就能看出两个明显的变化:实体经济成分加重,面向未来的布局。GE的这个战略一方面便于它发挥自身优势,另一方面也显然符合美国的利益,应该讲是明智的。如果这件事是发生在30年前,那么GE完成这样转型成功率是很高的,因为历史上GE易然庞大,但是从来不缺乏创新力,而且它的创新不是停留在一两项技术和一两种产品上,而是整个行业的创新。在过去历次技术革命中,GE都没有落伍,这简直是个奇迹。但是放到今天,GE再一次完成转基因的难度则要大得多,因为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倬得GE在工业制造上的很多优势在逐渐丧失,而美国也已经无法提供大量高素质的产业工人来振兴其制造业了。
GE作为全球业务最广、人数最多、产值最高的公司之一,能够下如此大的决心自我更新,可以说是具有非凡的眼光、胆识和魄力。或许十年后,我们会发现GE在那些新的业务中又成为了全球的佼佼者,这要感谢它在今天甚至更早几年的布局。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整个美国的衰退让GE覆巢之下没有完卵。我们这本书从当年“Google黑板报“的博客算起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大家对“浪潮之巅”这个概念已经普遍接受了。在这十多年里,其实我还在想另一个维度的“浪潮之巅”,就是浪潮在空间的位置,显然它现在正在从西方往东方转移,地处东方的公司天然地处在这一波浪潮之巅,但是GE却身处西方。因此,如果它这次转基因失败,更多的原因恐怕来自它所处的国家大环境。
在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之后,很多公司的负责人询问我,自己的公司如何才能像3M或GE那样通过不断地转基因,进入新的领域,从而做到长盛不衰。遗憾的是,我也没有很好的答案,毕竟世界上转基因成功的案例少,不成功的情况是常态。吴晓波先生在《大败局》一书中描述的诸多失败的例子,究其原因除了创始人自我膨胀不按规律办事外,转基因不成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吸取他们的教训,无疑可以减少重蹈覆辙的可能性。在过去几年里,我接触和看到了一些中国公司转基因不成功的案例,除了全世界公司都有的原因外,还特别有如下两点。
第一,公司负责人对自己的成功经验过于自负,尤其是在过去获得过成功的公司里。这种现象在跨国公司中也有,但是在中国更加明显。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每年GDP的增长平均都有7%—10%左右,IT领域的增长更快。而一个成功的公司一定会发展得比行业平均速度要快,几年下来,业务一定是十倍、百倍地增长。这里面固然有公司领导人英明的地方,却更有宏观经济红利的因素。但是,大部分公司的领导人容易把成功全部归结到自身能力上,这就如同基金经理永远把投资回报归结于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大盘增长和运气上一样事实上,一个公司的业务从几百万元发展到几亿元,大多数时候公司领导人的能力并没有增加一百倍。《大败局》一书中提到的很多公司创始人都有这个特点——业务能力没有随着业务提升多少。当他们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时,常常习惯于把过往成功的经验简单套用到新的业务上。且不说他们过去的成功运气成分占了大多数,即使在过去的业务中主要是靠自己出色的能力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拿到新领域中,大多不能照搬照用。因此,虽然这些公司的负责人都很聪明,在理性上是愿意接受新东西的,但是在内心却是抵触的,这是人性使然。
第二,一个成熟的公司多多少少存在着部门壁垒,在这个方面中国公司比跨国公司要严重得多。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公司中层甚至高层主管自己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常常是冲突而非一致的。一个30人部门的主管要想提升或加薪,最好的办法是将自己的部门扩大到100人甚至更多,即倬自己部门的业务对公司没有太大帮助,或者这种扩充会损害到兄弟部门的业务和公司的利益。在很多大公司这种现象就非常普遍。这也是人性的弱点,我们无法否认,也无法靠“教育”来克服。在多数跨国公司里,大家承认并正视这种现象的存在,力争在制度上杜绝这种将局部利益凌驾于公司利益之上的做法。在中国的公司里,一般不肯正视这种现象的存在,而领导层常常为了维护表面一团和气而默认这种(有损公司长远利益的)行为,这就造成了严重的抢地盘现象,并目构成部门之间的壁垒,那么整个公司就会对新业务支持乏力,转基因自然不可能,即倬公司的最高领导有这个远见。
相比这些平庸的公司,庞然大物的GE依然在努力转基因,非常值得钦佩,它不愧为一家伟大的公司。
GE公司大事记
1890——GE公司成立。
1896——GE公司上市,是道琼斯指数包含的第一批公司之一。
1913——发明X光管。
1917——发明电冰箱。
1919——GE成立无线电业务的子公司RCA,业务第一次成功扩张。
1926——GE成立合资传媒公司NBC,在很长时间里NBC是美国最大的新闻网。
1927——推出商用电视。
1930——发明洗衣机。
1932——进入金融市场,成立GE信贷;同年,公司获得第一个诺贝尔奖。
1938——发明日光灯。
1940——建立起全国电视网。
1941——推出喷气式发动机。
1954——推出洗碗机。
1957——建立全球第一个商用核电站。
1962——发明半导体激光器。
1981——韦尔奇担任CEO开创GE 20年高速发展;发明商用光纤材料。
1983——推出核磁共振机MRI。
1992——制造火星探测器。
2001——韦尔奇退休,GE进入平稳发展阶段。
2008——遭受金融危机打击,但是很快恢复元气和增长。
2018——GE被踢除出道琼斯工业指数。
结束语
科学技术是最具革命性、发展最快的生产力,一家科技公司要想在几次技术革命大潮中都能够立于浪潮之巅,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关键在于企业能否不断成功转型。受企业基因的影响,大部分企业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就有了新公司的兴起和老牌企业的衰退。一个跨国公司能像诺基亚那样做到一次成功转型已属不易,像3M和GE那样一百年来长盛不衰则更是凤毛麟角。3M是靠硬性的制度维持其创新,而GE是靠自身不断地淘汰现有的产业,同时开创新的产业。它们的成功经验已经成为了商学院教科书中的案例。有企业管理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一读《一个世纪的发明——3M的故事》(A Century of Innovation The 3M Story,3M公司提供免费电子版,可惜只有英文版)以及韦尔奇的两本书《杰克·韦尔奇自传》和《赢》。
第22章 生产关系的革命
1 股权结构和期权制度的本质
在生产关系中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即所有权、经营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利益的分配制度。在信息时代,特殊的股权结构和期权制度倬得公司的所有权和分配制度比工业时代要合理得多。在这一点上,工业时代的公司和信息时代的公司根本无法竞争。
在工业时代,资方(包括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公司的主人,他们不仅拥有公司的资产和生产资料,而目在经营活动中说一不二。很多工业企业的创始人是优秀的发明家或企业家,他们依靠自己各方面的过人之处,会缔造出伟大的公司,比如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爱迪生(GE公司前身爱迪生电气公司的创始人)、贝尔、西门子、克虏伯、本田宗一郎、盛田昭夫(索尼公司的创始人),都是如此。在白手起家那一代的他们,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管理上都是同时代的佼佼者,而在对内的管理上又常常是“暴君”(爱迪生、福特和本田宗一郎都是如此)或被送上神坛,但无论是哪种身份,他们都说一不二。如果他们犯了错误,是没有人能够纠正他们的。所幸的是,那些成功公司的企业家都具有超凡的能力,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知道他们,他们也就自然而然拿走了经营活动的主要利润。而那些能力有限的“暴君”们则早就被淘汰了,以至于我们对其闻所未闻。
在工业时代,资本的重要性特别明显,谁掌握了资本,谁就掌握了公司的经营权。19世纪末美国开始反垄断之前,金融资本渗透到工商业的各个领域,它们通过建立信托控制公司乃至整个产业,因此,那个时代下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唱主角的,是各个行业的垄断寡头。此后,易然美国的反垄断和进步运动让金融寡头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企业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简言之,依然是企业主拥有企业的全部,且说一不二。
1957年,肖克利来到旧金山湾区创办肖克利半导体公司。他一方面聪明绝顶,见识过人,另一方面则是一个十足的“暴君”,看问题带有很多主观偏见。有一次,办公室里丢失了一件小的办公用具,肖克利竟然为此要求员工们接受测谎实验。这种荒唐透顶的做法对于诺伊斯等知识型员工来说,简直是侮辱。倒不是因为肖克利本人有什么品性问题,事实上人们后来对乔布斯的非议甚至要超过他,而是因为那一代的企业家大多把企业当作了自己的私产。
到了菲尔柴尔德资助诺伊斯等人创办仙童公司的时候,他对公司的占有欲比肖克利好不了多少,因此当仙童公司盈利后不久,他便收回了全部的股权。这直接导致了仙童公司的分家。
公司的所有权通常直接决定了公司的分配制度。在工业时代,企业利润的分配基本上是一个零和游戏,雇员们多拿一分,资本家就少一分,反之亦然。当企业经营情况较好时,开明的资本家会出让一部分利润给员工,以换取员工的积极性。不过,这种脉脉温情在经济出现危机时会瞬间消失。历史上,亨利·福特是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的倡导者,这一点经常被一些他的崇拜者津津乐道。但是,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他就马上显示出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另一面,而目培养了几个专门对付工人运动的打手(也称为福特三凶)。二战之后,左翼运动兴起,工会开始在劳资纠纷中占据上风,他们永远以罢工和打官司为要挟,不断要求企业增加工资和福利。对于工会会员来说,公司经营的好坏并不重要,他们更关心的是能不能涨点工资。如果他们觉得罢工和谈判比努力工作更能让自己涨工资,就会毫不犹豫地采用这种方法,这也是工会的武器。因此,美国一些工会比较强势的行业,总是走不出“破产保护一一违约—一清除不良资产和员工福利一一重新盈利一—过度福利一一破产保护”的怪圈。在美国的传统企业和欧洲的大部分企业中,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日本企业没有那么大的劳资矛盾,但是企业和员工之间在利润分配上也跳不出零和游戏的圈子。
在工业时代,创始人、企业家以及投资人,他们通常代表着最新的技术和管理理念,他们的知识、经营经验和资本对于企业的成败至关重要,而工人通常只掌握着简单的技能,是可替代的劳动力。然而,到了信息时代,知识在经营活动中的重要性陡然提升,资本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资本方想要再通过资本拿走公司全部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就变得不合时宜了。肖克利半导体公司的八名主要雇员都是技术专家,其中六名是博士,在过去的企业中是不可能有这么高比例的知识型员工的。在公司里,诺伊斯和肖克利关于江崎晶体管的争议,属于两名世界级专家的学术争议或说技术争议。这种事情过去在爱迪生的公司、福特的公司也都发生过,而爱迪生和福特的处理方法则是简单压制甚至赶走威胁到自身权威的人。但是,这一套在肖克利手里就行不通了,不需要他的驱赶,诺伊斯等人自己就先走了。而由于他们的知识很值钱,洛克和菲尔柴尔德等人才会主动帮助他们。
在工业时代,生产成本是很高的,利润率相对偏低。谁更懂经营管理,更善于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谁就能在竞争中获胜。到了信息时代,半导体产品的成本是很低的,用诺伊斯的话讲,原材料都是些不值钱的沙子和金属,竞争将转向制造工艺,这时技术和知识的重要性才凸显出来。只有当创始人、金融家和主要员工共享公司的所有权时,才能让公司真正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因此,从硅谷的半导体公司开始,像这样来分配公司所有权的股权结构就成为初创公司融资时的普遍策略。
在硅谷,一个发展顺利的公司从初创到上市,创始人和投资人股权的比例需要大致相当,如果一方股权太大,则会失去平衡。如果创始人的股权占比太高,将显示其融资不足,结果是其发展的速度会受到限制。我们在前面章节提到的70–20–10律中讲到,在信息时代,由于科技公司的制造成本在收人中占比很低,因此很容易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发展不够快的公司则完全没有赢得市场大部分份额的可能性。此外,世界经济每隔8一10年会有一个下行的调整,如果一个初创公司没有一定量的资金储备,遇到经济周期下行阶段(也就是“寒冬”),常常无法坚持到下一个上行周期(即俗话说的难以过冬)。相反,如果创始人股权占比过低,投资人股权占比过高,则创始人的积极性常常难以被调动,如果遇到经济的下行周期,资本方会比较短视地贱卖公司以收回投资。除了投资人和创始人,员工特别是关键员工的利益也必须得到保障。通常,一个好的科技公司在公司上市前,员工的股权占比会在10%一15%之间。
如果仅仅有股权激励,它依然只是一个零和游戏,因为上述三方中一方的份额增加,另外两方必定减少,更重要的是当公司上市之后,公司便不能随意增股了,因为那样会稀释每一股股票的价值,让已有的股东利益受损。因此,为了保证三方能够形成合力,硅谷的公司普遍采用了增发期权(Option)的方式解决利益分配的问题。
期权不是股票,它是一种特殊的金融合约,是合约的一方在一定期限里给另一方按照某个价钱购买(Call)或出售(Put)股票的权利。比如,苹果公司的股票(代号AAPL)在2018年4月6日的收盘价格是每股168.38美元,该公司或某家证券公司(Underwriter)给予期权的所有者在1年内任何时候,以这个价格(称为执行价格,Strike Price)买进苹果公司股票的权利,也就是买人期权(图22.1)。如果在1年内股价从来没有超过168.38美元,期权的持有者不用做任何事情,既不赔钱也不赚钱。如果股价超过了168.38美元,那么不管股价涨到什么地步,期权的拥有者都有权以168.38美元的价格买入股票,从而赚取这个价格之上的溢价。因此,期权的持有者是稳赚不赔。而对于现有股票的持有者来说,他也并没损失什么,因为如果股价不涨,期权就作废了。图22.1显示了股价和期权利润之间的关系,当股价达不到期权授予的价格时,期权的利润为零,当然握有期权的员工也不会损失什么。当股价超过期权授予的价格时,期权的收益和股价是1:1的线性增长关系。
168.38图22.1 股价和期权利润的关系
如果一个公司的业绩增长达不到市场预期,股价就不会有明显提升,甚至会下跌,这样的期权就不具有价值。期权的价值是靠公司里的所有人,从老板到员工集体的努力来实现的。期权要想不变成废纸,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利润的提升,让市场肯定公司的表现,推动股价上涨。因此,期权所分配的其实不是存量利益,而是增量利益。一家公司里拥有期权的老板和员工,有足够的动力一起努力,把公司办得更好,让公司的股价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现有股东、老板(创始人和高管)以及员工,他们的利益就是一致的,而不再是零和游戏了。
期权的本质是两个契约。首先它是公司和现有股东(包括投资人和公司内的持股者)在监管部门的监督下所签署的一种契约。当被授予期权的老板和员工行倬(Exercise)期权后,这家公司就要增加流通股,因此一个公司不能随意发放期权,否则股价一旦超过可以行权的执行价格,就再也涨不上去了,这样就损害了投资人的利益。一家在美国注册的公司能发放多少期权,需要董事会通过;如果是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还要得到美国证监会报备批准,同时还要按照期权的市场价格计入公司运营成本。因此,这种相互的认可就是一种契约。一家公司可以发行的期权数量(或者比例),由公司未来的业绩增长速度而定。业绩的增长必须超过期权增加的比例,这样市场就不会做出抛售股票的反应。当然,为了保持公司团队的稳定,并目让公司里的每个人都能把目标制订得长远,公司里期权的期限通常是十年。
其次是公司里所有人之间的一份契约。在获得董事会同意发行一批期权之后,每个人的分配比例,实际上是一个契约合同。一家公司可以被理解为在某个行业里已经打下一定基础的经营实体,它为公司里的所有人包括管理者和员工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平台,而管理者和员工以前的经验和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市场资源、技术专利等),以及今后对这个平台的贡献,占有这个平台未来一部分收益。每个人所占有的那一部分的收益大小,就是他们通过谈判获得的期权数量。
期权制度的直接作用是合理分配未来的财富,但它同时也改变了公司里人和人的关系,从过去工业时代那种雇佣关系,变成了一种基于契约的合作关系。过去,一个部门经理通过权力多拿走10万元的奖金,或者多给那些喜欢拍马屁的人1万元奖金,这些奖金马上就兑现了。但是,倬用期权作为分配工具后,结果就不同了,如果部门经理给自己或亲信多发了期权,而把像诺伊斯和摩尔这样的能人排挤走了,他最后的收益将是零。
我在国内几所著名的商学院讲课时,很多企业家学员抱怨如今招人太难,留人更难。我进一步了解后发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信息时代依然采用工业时代的生产关系进行管理。在分配利益时,总认为这是企业对个人的恩赐。实际上,今天资本已经不再是稀缺资源了,人的才智更具有难以复制的稀缺性。一家信息时代的企业,应当是一个给每个员工发挥特长的平台,要“请”个人来做事情,要本着企业与个人合作的心态,做不到这一点,要想留住人确实不容易。
同样的道理,在信息时代聪明的员工懂得为自己寻找一个好的发展平台,并目摒除个人好恶和情绪积极地为那个平台工作。在硅谷的大部分公司里,工资只是相当于生活费,在硅谷这个消费水平非常高的地区只能保证简单的衣食住行;而对于成功人士和高收人人群来讲,期权才是他们获得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获得有价值期权的途径就是加人一家有发展前景的公司。事实上,在当下中国的北京、深圳和杭州那些房价极高的地区,很多生活优越的工薪阶层,他们主要的财富来源也是百度、腾讯和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的期权,而他们看似不低的工资,累积100年也买不起当地一套好的住房。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分配制度的变迁。
综上所述,自信息革命发生以来,公司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制度必然会导致公司内部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特征有这样两个:
首先,从过去所谓的主管、领导、老板为核心的文化,变成了以专业人士为核心的文化,其代表就是很多IT企业中的“工程师文化”;
其次,上下级的关系由过去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变成了契约合作关系,底层员工主动参与一部分管理,导致公司管理的扁平化。
2 工程师文化
工程师文化其实是欧美专业人士文化的一个缩影,而在信息时代它的重要性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于是工程师文化就成为了硅谷企业新型生产关系的一个明显特征。
什么是工程师文化?我们不妨先看一看它在硅谷企业中的具体表现,然后再来总结它的定义。
工程师文化首先体现在这一群人的地位高。Google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工程师文化的公司,它的创始人佩奇在公司大会上明确地说,工程师在公司里的地位处于金字塔的顶尖,过去如此,未来也永远如此。在硅谷,佩奇的观点具有普遍性,工程师的社会地位确实很高,很受人尊敬。
当然,一种职业受人尊敬,人为地强调它的地位高是没有用的,必须要有一种机制保证他们的收人很高,这样最优秀的人才有动力从事相应的工作。图22.2给出了2013年硅谷和美国其他地区主要科技公司中软件工程师的基本工资数据,并对比了美国收人最高的两个职业(外科医生和公司高管)、名牌大学正教授、时任美国总统和时任加州州长的收人。需要指出的是,科技公司里的工程师除了基本工资,还有奖金和股票(或者期权的收人),根据公司情况和员工职级,这部分收人可能为基本工资的10%到数倍,像Google或Facebook这样的公司,奖金和股票的平均水平不低于基本工资的60%,这些公司的工程师的年总收人超过政府高级官员的年总收人,与斯坦福、哈佛或麻省理工等名牌大学正教授的年总收人相当。
图22.2 2013年硅谷和美国主要IT公司软件工程师的基本收入与其他行业从业人员收入的对比
除了收入较高,工程师的工作也比较稳定,公司裁员时最后才可能裁撤到工程师。另外,他们的工作时间比较灵活,每年的休假比较多,很多人愿意做一辈子工程师,这使得美国公司里一线工程师的平均工龄比中国公司里同样职位的工程师要长很多,经验也自然更丰富。这一点在硅谷的公司里更加明显。
在硅谷的另一些公司,比如Facebook和苹果里,易然看上去好的产品经理地位最高,其实他们大多是工程师出身。而在半导体公司,基本上只能让工程师们说了算,因为半导体相关的专业技术非专业人士看不懂,甚至半导体的销售常常也需要由主管工程的副总裁负责。当然,工程师文化对硅谷创新所起的作用远不止体现在工程师的地位高,一个公司要想通过简单地提高工程师的地位和收人就获得硅谷那样的成功,可能会失望,因为工程师文化其实反映的是硅谷公司在管理和做事方法论等方方面面的特点,而不仅仅是收人。这就涉及工程师文化的另外几个特点了,这里我们重点谈其中的两个。
先说说“动脑和动手”。
这五个字其实是被誉为美国工程师摇篮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它从一个侧面诠释了工程师文化。一个合格的工程师,必须能够自己动手解决问题,而不是让别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大家可能听说过DIY这个词,它是Do It Yourself的缩写,这也是工程师的最基本要求。有些人觉得有个工科学位,在IT公司里能够写两行代码,名片上印着工程师的头衔,就算是一个工程师了,其实工程师远没有这么简单,或者说没那么容易当。一个合格的工程师,至少应该能够独立地实现一项工程目标,不论目标大小。在国内的很多公司里,很多程序员需要产品经理告诉他们做什么,这样的人被称为“码农”一点也不奇怪。我虽然并不喜欢这个对工程师带有调侃的贬义称谓,但是有时想想,很多自称为工程师,或被公司任命为工程师的人,确实用“码农”来称呼更合适一些,因为他们的确在从事不太费脑筋的工作。这些人和我要说的工程师的差别在于,前者缺乏后者那种发现问题并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主管很难放心地将一件工作交给前者后就不再管了。
……
这张表很好地反映了硅谷工程师的一个特点—一他们不是科学家,没有做太多基础研究(至今麻省理工学院以及东部不少顶级大学对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依然看不太上眼),但是他们对新技术有非常强的好奇心,而且有自己动手做小玩意的激情,于是他们把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现有的产品中,或者自己拼拼凑凑,搞出一个从来没有人想到过的新玩意儿。这些自己动手做的小东西,很多可能失败了,不过大量的硅谷工程师每天都在不断地做各种各样的尝试,总能做出一些改变世界的产品来。
安卓操作系统发明人安迪·鲁宾(Andy Rubin)的工作就是典型的“自己动手用现有技术做小东西”的过程。Linux操作系统早就有了,简单的手机操作系统也早就有了,但是将体量庞大、消耗资源多的Linux用在手机上,之前尚无太成功的先例。于是,鲁宾就把这些现有的技术搭起来,做了一个小玩具,他把这个小玩具称为安德鲁的小东西,并且用自己名字(Andrew)的前几个字母Andr和小东西的词根-oid拼凑出一个新词Android,即安卓的英文名称。
像鲁宾这样捣鼓小东西的人在硅谷比比皆是。需要指出的是,做这些事情通常不是老板下达的任务,而是出于自己的兴趣。正是发现工程师有着巨大的创造力,瓦伦丁才决定创办红杉资本来帮助他们。在瓦伦丁看来,只要给一些动手能力强的工程师注资,让他们全职地将自己DIY做出的小东西变成产品,就一定能改变世界。
既然是自己动手,那么自己就要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命令别人替自己做事,这是硅谷工程师的特点。在硅谷你总是能看到一些世界科技行业的泰斗或巨头还在写程序。Google的狄恩(Jeff Dean)博士和戈玛瓦特(Sanjay Ghemawat)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云计算技术的工程师,也都是美国工程院院士,至今仍在自己写代码,而且每次有什么新的想法,都是自己先实现自己的“狗食”(Dogfood)
Google的汤普森是UNIX的发明人、图灵奖获得者,每天大部分时间依然花在写程序上。太阳工作站的发明人,该公司的创始人贝托谢姆,后来成为了天使投资人,又投资成立了上市公司Arista,今天依然在写程序。和我一起做投资的朋友、Hotmail的创始人史密斯(Jack Smith),在把Hotmail卖给微软之后,曾经担任过一家上市公司的CEO,后来做投资,现在每当有什么好想法,依然会坐下来自己写程序实现它们。这些人可算是功成名就,要是放在中国,或许早就当官去了,至少也进人到“君子动口不动手”的状态,但是他们在硅谷依然在自己动手。易然他们自己写的代码未必比别人好多少,但是这在硅谷营造了自己动手的工程师文化。《纽约时报》曾经对比过微软和Google在研发上的差别。在微软,那些负责发明创造的研究员是动口不动手的,有专门的研发工程师为他们实现自己的想法;而在Google,没有人替你写程序,所有的想法都需要先由自己实现证明。这样一来,两个公司在开发上的效率就有了巨大差别。
硅谷工程师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不仅要会动手,更要会动脑。在很多公司,产品经理和工程师是两个独立的角色。在中国的一些互联网公司里,有着大量的产品经理,在个别项目上产品经理甚至比工程师还多。这样的搭配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恶果,首先很多产品经理不得不去做那些本不该由他们来完成的细节设计,同时本该参与产品设计的工程师在设计上完全懒得动脑思考。另外,产品经理可能会因为缺乏对工程技术的了解而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而工程师也会因为缺乏对产品的全面了解,做的东西达不到产品经理预想的要求。在硅谷的公司里,产品经理和工程师的比例非常低,在Google这样的公司或者半导体公司里,这个比例可能是1:20,甚至比1:100还低。在我第二次回到Google时,辛格(Amit Singhal)博士为了动员我加人他的部门,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他的部门有一大优势:“在我管辖的部门里,产品经理和工程师的比例是1:200多。”这个比例也许有些过低,却反映了硅谷以工程师为主导的特点。
有人或许会问,产品经理的比例如此之低,那么谁来设计产品。很简单,工程师会做很多在中国的企业看来应该由产品经理做的事情。讲到这里,就必须说说什么是优秀的工程师,什么是平庸的工程师了,他们之间是有着巨大差别的。工程师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承认这一差别,并目对不同水平的工程师区别对待。
能够比较清晰地解释工程师之间差别的工具,是苏联著名物理学家朗道(Lev Landau,1908—1968)提出来的朗道等级。朗道曾经根据物理学家的贡献把他们分成了五级,每一级之间的贡献相差一个数量级。按照朗道的划分,只有玻尔、狄拉克等少数物理学家属于第一级。其实对于工程师或者任何一种专业人员,也可以做同样的划分。如果我们按照朗道的方法把工程师分为五个等级(图22.3),每一级的能力和贡献大致可以总结如下。
图22.3 工程师的五个等级
第五等工程师,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能够独立设计和实现一项功能的人。这是对工程师的基本要求,如果一个人只是懂一点工程实现的手段,需要别人告诉他怎么做,那最多算是助理工程师或者技工,不在我们讨论的工程师之列。
第四等的工程师就需要有点产品头脑了,也就是说他们在做一件事之前,要知道所做出来的东西是否有用、易用,是否便于维护,是否性能稳定,等等。除了要具备产品设计方面的基本知识,还要具有一定的领导才能,能在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从头到尾将一个产品负责到底。这在很多硅谷的公司里,基本上是一个高级工程师所应有的基本素质。对大部分工程师来说,这些素质不是一个工学院就能培养出来的,而是需要在工业界实际锻炼三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当然,个别天赋很好的年轻人在学校里就具备了这种素质,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
第三等的工程师,可以做出行业里最好的产品。他们与第四等工程师有着质的差别,这不仅反映在技术水平、对市场的了解、对用户心理的了解以及组织能力等诸方面,而目也反映在悟性的差异上。当然,这种悟性很多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但这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了。有些人从工作一开始,可能需要十年八年,经过多次失败,不断总结,终于在某个时间点豁然开朗。而另一些人可能非常幸运,在一开始就有幸和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加上善于学习,五六年下来就能达到第三等的水平。在硅谷,有极少数工程师只花了五六年时间就达到了这个水平。但是,即使一个人再聪明,基础再好,也需要在工程上花足够的时间才能达到这个水平,一个年轻人工作了四五年就开始做行政管理工作,基本上就和这个水平无缘了。
第二等的工程师是那些可以给世界带来惊喜的人,比如实现第一台实用化个人电脑的沃兹尼亚克、DSL之父约翰·查菲、iPhone和Google Glass的总设计师,以及前面提到的鲁宾、狄恩和戈玛瓦特等。他们与第三四五等工程师的差别在于其工作的原创性以及对世界的影响力。当然,他们的工作不是科学研究,这一点和科学家毕竟不同。
第一等的工程师是开创一个全新行业的人,历史上有爱迪生、特斯拉、福特,二战后有保时捷(Ferdinand Porsche,1875—1951)博士、本田宗一郎(1906—1991)和硅谷的诺伊斯等人。这些工程师不仅在技术和产品等各个方向上与第二等的工程师有了质的差别,而目在经验和管理上也是好手,他们通常也是企业家,并通过自己的产品改变了世界。这一类人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正如朗道列出的第一等物理学家只有个位数一样,第一等的工程师也是如此。朗道认为每一等物理学家之间的贡献相差十倍,而每一等工程师的差距也有这么大。当然,很多企业家都希望能遇到一些第二等甚至第一等的工程师,但是这需要一个由工程师构建的完整金字塔:要想出几个第一等的工程师,就需要有足够数量的第二等工程师作为基础;同样,产生第二等工程师要靠大量的第三等工程师作为基础。在一个产业里,不可能指望在一大堆第五等工程师的基础上,突然冒出一两个第一或等者第二等的工程师的。甚至有时,即使高薪聘请来一个第二等的工程师,如果没有第三、第四等的工程师与之配合,他也很难直接依靠第五等的工程师做出一流产品。
在硅谷,人们能够有幸接触到第二等工程师,这些人有时决定了一个公司的产品所能达到的高度。而在公司里,真正干活的主力是第三、第四等工程师,这一类人比较多。但在中国的一些IT企业里,大家喜欢当官,因此在第五等工程师之上,会出现断层,从而影响产品开发的质量和原创性。
硅谷工程师文化的第三个特点是全社会对工程师的认可。这种认可不仅包括对工程师的尊重,以及给予他们较高的社会地位,还包括允许不同等级的工程师在收人上有巨大差异。既然每一等工程师的贡献可以相差十倍,为什么他们的收人不能够相差十倍?当然很多人会反对这种收人差距过大的做法,比如欧洲的社会党人和美国的工会。但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拉大收人差距能够最大程度地发展生产力,而平均主义不能,那么采用前一种分配方式的地区无疑会获得更快的发展,硅谷就是这样的地区。
在硅谷的很多公司内部,不同层级、不同贡献的工程师之间,工资和奖金的差异其实不大,但是期权起到了调节他们收人的主要作用。这使得第二等工程师的收入真的可以比第三等工程师多出一个数量级,而第三等和第四等之间,收入可能也有数量级之差。很多企业请我推荐,想要招聘一些Google的工程师,而目张口就要最好的,但我明确表示那些最好的工程师所要的薪酬包大部分公司可能都付不起,因为在大部分企业的想象中,不同的工程师之间收人差距在两三倍就算是很多了,而在硅谷的明星企业,这种差距是数量级的。在金字塔尖的那些工程师的收入非常高,甚至高过高层管理人员,再加上社会对他们的认可,这些人转行政管理岗位的欲望并不强烈。在硅谷的公司里,工程师们有专门的上升通道,而硅谷的工程师文化也由此得以很好的维持。
介绍完工程师文化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了,到底什么是工程师文化?
简单地说,工程师文化有两层含义,首先在于,它强调了一个机构或者一个社会以工程师为核心创造未来的价值。历史上,有过以土地的拥有者为核心、以资本的所有者为核心、以商人为核心构建价值体系,但是在以硅谷为代表的信息时代,需要以工程师为核心构建价值体系。接下来,既然工程师是创造价值的核心,那么他们必须具有主动性,不断承担越来越多的使命。由于人的能力有大有小,贡献会有巨大的差距,这样也会直接导致他们的收入有巨大差距。只有正视这种差距,接受这种差距,才是信息时代应该有的思维。
硅谷工程师文化的形成有欧美历史上的原因,也有硅谷本身的原因。从历史上讲,欧美国家在历史上很少有大一统的帝国,官员的重要性就要小得多,专业人士的地位相对比较高。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对工程师远比中国尊重和重视,比如在法国要取得工程师的资格,难度很大,需要在大学先读预科,然后才能进人好的工学院获得工程学位,并成为大公司的工程师。相比之下,一些中国人的官瘾比较大,非常看重级别。有一次在一个活动中,一位中国来的总领事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大使级”(总领事)这个形容词,言下之意他是副部级干部。不过,我在类似的活动中遇到过朱棣文和骆家辉等人,他们给我们的名片上可没有写过“部长级”教授或“部长级”大倬之类的名称。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即倬一些学者,给我的名片还一定要印上享受政府津贴或者千人计划等称谓。社会精英都是如此,在公司里谁要是没有一个行政级别,脸上都会觉得无光。
当然,硅谷工程师文化也有它本身的成因,主要是公司所有权和分配制度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员工特别是核心员工和公司都是一种契约关系,因此行政职务和汇报关系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这一点在中国目前还做不到。我接触过很多中国的工程师,他们想当官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作为一个工程师,他们完全感受不到自己能拥有公司的一部分,这和硅谷的工程师不同。因此,他们只有当了官,有了一批围着自己转的下属,才能感觉到自己对公司的影响力。硅谷工程师也看重一种级别,就是他在朗道等级上的位置,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他承担的职责、收入以及在别人眼里的分量。
在美国东部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工程师在收人上差异很小,这就无法激励他们往更高的层级努力。因此,在那里的公司中,第四等和第三等的工程师数量很多,但缺乏更高级别的工程师,因而很难做出改变世界的发明创造。这其实是欧洲很多国家创新力不足的原因,而那些国家的工程师若是到了硅谷,则能做出大得多的贡献,这充分说明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性。
在信息时代,很多专业机构内的文化和硅谷的工程师文化其实很相似,只是会计师、律师、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的作用代替了工程师。其本质还是一种基于契约的生产关系。
当每一个工程师都具有很高的自觉性时,管理也就变得容易了。公司为了提高效率,愿意将管理的层级扁平化。
3 扁平式管理
扁平式管理这个词大家并不陌生,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整个公司管理的汇报层级少,这一点对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和工作效率至关重要,这也是很多企业一直追求的目标。
曾经担任过Google工程总监的张智威博士,在上个世纪末任职于当时的世界第二大计算机公司数字设备公司(DEC)。他讲到这个曾经的科技明星企业到了后期官僚主义有多么严重。据他介绍,该公司曾经出现过上下九级只有一个单一汇报人的奇葩现象,即一个高级副总裁手下只有一个副总裁,后者手下只有一个资历更浅的副总裁,这位副总裁下面只有一位高级总监,以此类推,最后由一位一线经理指挥仅有的一个工程师。数字设备公司的例子易然有些夸张,但这种现象在大企业中并不少见,从管理的顶级到最底层的员工,中间有七八级,是颇为普遍的现象。
这种多层管理层级通常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公司历史越悠久,一般这种现象越严重。它的危害其实很多管理者都很清楚,但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任何改变都要剥夺一些中高层管理者的利益。在美国一些传统的企业和中国的很多企业里,较高的层级成为很多人的荣誉甚至奋斗的目标,因此,公司的创始人或者CEO明知这种组织方式会导致低效率的管理,却无法将管理层级扁平化。
硅谷企业的管理层级相对较少,这里面有历史的成因,有出于管理效率的考虑,还有一个硅谷所特有的原因,即它那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妨从这三个方面看看为什么硅谷企业能够做到管理的扁平化。
首先,来到硅谷的人目标都比较明确,就是寻求个人做事上的发展,而非在做官上的成功,整个社会没有太多的官本位文化。人们到硅谷住上一年半载,就会发现在这里,一个明星公司的普通员工,甚至比一个发展缓慢公司的副总裁更受人尊敬。比如这两个人同时离开公司去创业,前者通常更容易获得投资人的垂青,甚至两个人同时去购房,卖方的经纪人常常对前者会更感兴趣。一个明星公司的工牌,通常比一张头衔吓人的名片更有用。
其次,在同等收入规模的公司里,硅谷公司的规模相对较小,人数较少,整个公司的层级较少也很自然。加上硅谷公司的生命周期相对较短,很多公司在官僚体制还没有膨胀到很臃肿的程度,就已被收购或者关闭了。因此,大家在习惯上普遍不认同很深的管理层级。
最后,硅谷的公司管理层级较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被激烈的竞争逼出来的。我们在前面讲过,硅谷虽有光鲜的一面,更有竞争非常激烈、淘汰率非常高的一面,那些管理层级较高的公司通常会因为执行力差而率先被淘汰,而采用扁平管理方式的公司最终能生存下来。在外界看来,剩下的都是管理扁平化的公司。久而久之,新公司在成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一般都要采用扁平化的管理方式。
汇报层级少仅仅是扁平式管理外在的、最明显的特征,但如果单纯减少公司的管理层级,不调整相应的管理办法,还是没有用的。
扁平式管理的另一个特征则体现在分权上。在一个现代企业中,每一级管理者甚至个人要拥有最终决策的权力,同时承担一定的责任。一件事情一个员工自己就能决定,就无需他的经理或总监来拍板。一个经理或总监能够决定的事情,就不需要副总裁或更高职级的人来给意见。在Google,一名资深的工程师或产品经理,即使不担任任何行政管理工作,也能决定数万美元的采购,而不必先请示任何人。Google的一个副总裁可以决定数百万美元的市场活动开销、上千万美元的大宗采购或者基础建设,并有权给予员工大笔的股票或者期权。只有分权,才能真正给公司带来效率。
扁平式管理的第三个重要特征体现在限制上级对下级的人事权。如果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生杀予夺大权,那么他的下属就成了他的奴才,而不是公司的员工,而下属也会牺牲公司的利益以满足上级的意愿。这样的公司最终一定是山头林立,任人唯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公司的战略意图和行政指令必定难以执行。在真正施行扁平式管理的公司里,上级对下级通常只有人事上的否决权,而没有决定权。也就是说,他可以否决提升那些他认为表现不好的员工,但无法提拔那些只是他个人喜欢的员工。在这种情况下,下属与其取悦于上级,不如把工作做好取悦于所有人。另外,上下级之间是契约关系,上级对下级的调动没有任何的限制权力,因此一个中层主管为了维持自己团队的稳定,就必须学会尊重下属,而不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奴才。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中人和人之间的摩擦降低到最少。
扁平式管理说起来很简单,很多硅谷之外的公司也在努力将管理扁平化,但是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提高效率,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简单地说,就是那些公司在管理上其实是换汤不换药。
简单地把管理层级减少一两层不是难事,一个1万人左右的企业,如果每个管理者管10个人,从上到下五层也就够了,这已经比很多公司管理层级少了。但是,建立一个这样的管理层级并非扁平化管理的全部。一些公司的负责人确实将管理层级扁平化了,做了把普通员工到CEO之间的汇报关系从七层降低到五层这一类的表面文章,但本质上仍是换汤不换药。据我观察,在中国企业中,除了小米科技等极少数新一代的企业做到了扁平化管理,大部分公司内部管理并不是真正扁平的,不论那些企业里的汇报层级有多少。甚至很多企业的老板只是想学一些皮毛,做点表面文章,让员工感觉和大老板之间的距离近一点,舒服一点而已,他们从内心里并不打算真正这样去管理公司。
在国内不少大型互联网公司和其他科技公司中,半吊子的扁平式管理十分普遍,当然很多传统的企业连这也做不到。其根本原因在于,大环境的因素、官本位文化、人与人之间契约精神的缺失,造成了公司的管理依然非常传统一一内部层级森严,部门间壁垒严重,上下级之间扁平式管理是有名无实。这主要体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公开场合可以强调行政等级。比如在开大会时,会场的座位就分为了三六九等,参会级别最高的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座位前还有个桌牌;第二等级别的领导坐在第一排,有桌子有茶水;第三等的领导坐在前面比较好的预留位子。其他员工在后面和旁边随便坐。再比如,各级人员的办公场所完全与职级挂钩,中层以上的干部享受独立办公室,高层干部拥有豪华办公室,有些公司的CEO或者创始人甚至一个人占几层楼,而员工则挤在小隔间里,甚至有些新来的员工要在过道里临时搭个办公桌办公。
这些一眼就能看到的差异向所有员工传递出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你们不平等,第二个信号就是你们需要在职级上往上爬,第三个信号是一旦职级比周围人高,一定要搞些特权显出自己的地位。
公司和员工之间缺少正常沟通的渠道,原本很多信息可以由公司直接传达给全体员工,却要通过上下级关系层层下达,这样无疑在向每一个人强调人和人之间是有层级差异的。
各种福利、津贴、差旅标准因为职级不同,差异巨大。这虽然不像第一种情况那样每天都在提醒大家层级的存在,但客观上促使大家将注意力集中在往上爬上,而不是做事情上。此外,高级管理层还享受很多对基层员工并不公开的待遇,但是人事部门和秘书们嘴其实又不严,这些待遇便成了公开的秘密。
上级对下级拥有过大的人事权,从招聘、考核评估到提升无不由上级说了算,导致下级过分看重直接领导的态度,而不是公司的利益。上级也会把下级员工看成自己的私产,并且为了提升自己在公司的地位,不断扩大自己下属的人数。同时,上级还对内部调动的下级进行打压,每次都将最差的考核评分给予那些希望流动的员工,令这些员工因业绩考核记录不良而难以得到提升。
分权不够,很多事情都需要层层审批,比如招聘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有时还需要副总裁面试,招聘一个总监,需要公司的CEO面试。再比如在财务上,一个年收人几百亿的公司,居然花费一百万元也需要CEO审批。
这类虚假的扁平式管理的特征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所有这些做法,无不在向各级员工传达着一个信息,那就是每一级之间都有一个鸿沟,每个员工自己会因为比下级高出一等而在下级面前感觉良好,同时每天工作中的很多事情又在时时刻刻提醒他和上级的不平等。这样,大家工作的目标就变成了当官往上爬。这也导致大量的年轻人在刚刚熟悉业务后,就不愿意从事一线的开发工作,而要削尖脑袋挤进领导岗位,在一线具体做产品的则永远是工作经验相对较少的新员工。在IT的很多行业里,如果没有经验丰富的老兵,是做不出来一流产品的。比如在半导体制造方面,不是花钱收购一条先进的生产线就能量产出半导体芯片的,需要有至少十年经验的资深工程师调试并掌握关键的生产部门,在一个人人都想当官,没人愿意成为专业人士的企业里,这件事就很难办到。
遗憾的是,市场并不因为大环境的因素和官本位文化就照顾那些壁垒森严的企业。因此,一些发展比较好的科技公司有扁平化管理的意愿,特别是在要和国际接轨、开拓海外市场的时候。但是,因为不理解信息时代新的生产关系,包括人和企业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以至于出现上述换汤不换药的现象。
那么扁平式管理的本质又是什么呢?简单地讲,就是用契约合作精神,代替工业时代很多传统企业中的那种隶属关系或者拥有的关系。
硅谷喜欢用“婚姻”这个词形容一个人加入一个公司的行为。既然是婚姻,除了相䶼的吸引和认可,重要的是一种契约,也就是说员工要履行他们对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公司则为他们的发展提供空间,并目根据这个人的表现(包括对公司的贡献),从公司的收益中得到应当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个人的收益并非像很多硅谷以外的公司那样,是以市场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加上老板对他的满意程度给予的奖金而确定的,而是根据他个人对公司的贡献,按照事先定下的契约,从公司的利益中分到一部分。每个员工都很明确,他是被这个公司所雇用的,与公司有契约,而不是被哪个老板所雇用成为老板的人。在工作的过程中,上下级之间通常是用一种商量的而非命令的方式沟通。员工和他的主管上级之间没有这种隶属关系,因此员工的流动就得到了保障,只要一个新的项目需要人,他就可以离开现在的组织机构加人新的项目,而他的上司则无权干涉。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那种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现象。
每个员工和公司都是一种契约关系,不论职级的高低,人与人之间相对都是平等的,而目几乎所有员工的福利都是相同的,并不存在太多对高层管理者的特殊照顾。以Google为例,很长的时间里,共同创始人布林一直和大家一样,出差坐飞机的经济舱,而各个级别的人出差时所住的酒店档次也是相同的。当Google公司的经营稳定后,所有员工出差都能享受五星级酒店的待遇,那些职级较低的年轻员工也能感受到公司给了他们和老板们同样的关怀。
图22.4 扎克伯格没有固定的办公室,他办公的地方通常就是空闲的工位
到硅谷参观的很多中国代表团,都想去看看各公司CEO的办公室,结果他们大失所望,因为在几乎所有的公司里,这些高管们的办公室都很寒酸,有些甚至还没有办公室。特斯拉公司的创始人马斯克就在公共办公区里划出一片相对较大的工位办公,用的都是美国最便宜的宜家家具。美满公司除了CEO有一间办公室,其他上至CTO和CFO,下至普通员工,都坐在开放的办公区里。而Facebook的扎克伯格,甚至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图22.4)。Google的佩奇易有自己的办公室,但是很多高级副总裁都在和别人共享一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办公室。我每次和辛格博士开一对一的会议,都不得不到办公楼的园区里一边散步一边谈事情,因为他是和4位副总裁分享一个不大的办公室。办公条件上的这种设置,使得公司里的所有人都能真正感受到管理是扁平的。
硅谷公司里不同职级的人,比如存在汇报关系的上下级,他们在待遇上的区别主要在于基本工资,以及当初和公司谈好的股权。一个员工,如果经验比较丰富,资源比较多(比如手上掌握的技术、管理经验或者客户等),与公司签署契约时自然可以获得一个比新员工有利得多的劳动合同。事实上,在硅谷的公司里,一些重要的岗位,比如CTO、CFO等,其劳动合同并不是公司老板和他们直接谈的,而是通过一个第三方的咨询公司根据这些特殊员工之前掌握的资源,以及他们在未来可能为新公司带来的利益,三方协商而定的一个利益分配方案。当然,每个员工到了公司之后,由于实际表现不同,作用不同,他们和公司之间的契约其实也在调整。不过,不管怎么样,他们的收入和管理的人数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在Google和Facebook等公司内部,有一些只管几个人的资深员工,待遇和收人不亚于那些在汇报关系上层级非常高的管理者。在这样的环境下,员工们对一个比较好听的管理职务的需求就大大降低了,这样一来管理的层级才能做到较少。
易然没有哪个公司的管理是十全十美的,但是扁平式管理的特色让硅谷的公司具备较强的执行力,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较强的应变能力。
4 轻资产公司
结束语
在信息时代,生产关系各个要素之间彼此的关系和地位相比工业时代有了很大变化。从整体上讲,和物质相关的因素的重要性在下降,和人相关的因素的重要性在提升。具体到人和人的关系,它逐渐从单纯的资方和劳方的雇佣关系、上下级的约束关系,变成为人和企业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契约关系。易然人和人的绝对平等还是做不到,但是这种相对的公平促倬企业内部的各种人都能为同一个目标努力。在利益分配上,信息时代的企业通过股权和期权激励,改变了原有利润分配的零和游戏,大家更多地是通过让企业超出市场的预期,而从资本市场获得激励。
今天,很多历史悠久的大型企业在和近年来崛起的新型企业竞争时,常常会感到力不从心。虽然前者通常有更多的资源积累、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储备,但是因为生产关系落后,特别是分配制度不合理,无法调动人的积极性,也无法快速适应产业不断的变化。总之,生产关系的问题不解决,再多的努力也会显得徒劳。
第23章 印钞机 最佳的商业模式
1 Google的广告系统
2 eBay 和亚马逊的电商平台
3 戴尔的虚拟工厂
传统的制造业需要通过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加工制造、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零售7个环节才能收回投资,获得利润(当然,产品需要市场推广和广告推销)。一个企业或投资人,需要先投人资金,然后经过这么一大圈才能挣到钱。所有的公司总是在尽可能降低各个环节的成本,以获得比同行更高的利润率。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人将工厂生产流水线的概念扩展到仓储运输和整个加工制造中,大大降低了制造业的成本。在很多日本工厂里,没有库存零件,当第一批零件用完时,第二批刚好送到,而第三批正在路上,第四批在上家的流水线上。同样,产品一下流水线,开往港口的汽车就已经准备装货了。这种高效率,使得“日本制造”打败了美国和欧洲制造,迅速占领了世界市场。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欧美日的大公司开始在东南亚和中国建工厂,将加工制造这个环节的成本压到了最低。
其实,最聪明的办法是直接减少其中一个或几个环节,这样资金从投人到收回最快,利用率最高,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计算机制造商戴尔,它将上述7个环节减少到2个,从而打败各家兼容机厂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商之一。
戴尔公司以其创始人迈克尔·戴尔的名字命名。和盖茨、乔布斯一样,戴尔也没有读完大学。和中关村无数攒PC的人一样,戴尔1984年还在奥斯丁的德州大学读本科时就开始攒PC卖。一个暑假他挣了一辆宝马汽车,尝到甜头的戴尔干脆退学专职攒PC,成立了戴尔公司。相比当时的IBM或兼容机的龙头老大康柏,戴尔公司没有什么技术优势可言。在20世纪80年代PC起步时,比戴尔大的兼容机公司不计其数。但是戴尔在商业模式上改进了传统制造业从设计到销售的过程,倬得戴尔计算机的价格比其竞争对手低得多,市场占有率渐渐成长起来,到2000年成为美国最大的PC制造商。和很多制造业外包一样,戴尔为了降低成本干脆不设工厂,而由东南亚(主要是中国台湾)的OEM工厂加工。这样,它就不需要投人资金建设工厂并维持工厂的开销。接下来,戴尔干脆将产品设计也外包了。攒过PC的读者会知道,PC的设计其实没有什么学问,和搭积木差不多。至于原料采购,戴尔每年和英特尔、AMD、希捷等几家主要的PC芯片和配件生产厂商谈好协议,由这些公司直接将货发给那些OEM厂,便省去了原料采购和一半的仓储运输环节(计算机成品从OEM厂到顾客的仓储运输现在尚未省去)。最后,戴尔在销售渠道上做文章,将批发和零售商的利润降到最低。
像计算机这样的产品,过去设计、制造和销售(包括市场推广)分别占售价的三成、三成和四成。也就是说,零售价10000元人民币的计算机,制造成本只有3000元,开发成本也大致这么多,而广告和批发零售的耗费和利润占掉了4000元。现在戴尔把开发和制造的成本压到了最低,然后开始打批发和零售商的主意了。戴尔一直坚持直销,它基本上不经过批发商,在很长时间里也很少通过零售商分销。戴尔有自己的销售人员,负责向企业级的大客户推销产品。而对于个人和小企业,戴尔以前只提供电话订购、邮购和网上订购等购买方式。近几年为了和惠普争夺市场份额,戴尔才通过沃尔玛和好市多等连锁店出售电脑。戴尔的直销方式很简单,它向顾客发放各种计算机配置的价格表,价格比其他品牌计算机的零售价会低很多。很多顾客会被它的价格吸引,打电话或上网选一个型号并把自己的付款方式提供给戴尔就行了,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戴尔收到订单,直接通知它的OEM工厂。工厂每天按订单生产计算机,然后按照戴尔提供的地址发货。这些成品计算机根本不需要经过戴尔就送达顾客手中。这样戴尔将仓储运输的另一半也省掉了,因此戴尔根本不需要有仓库。像戴尔的这种直销方式不仅省去了批发和零售的成本,大大降低了产品的价格,而目在价格上非常透明,也省去了个人消费者讨价还价的麻烦。戴尔开发了一套在线的订购系统,一端顾客在上面填自己要买的计算机配置和个人信息,另一端自动通知工厂生产和发货,利润就自动流入戴尔公司了。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印钞机式的商业模式。戴尔只需牢牢控制住订单处理和零售(主要是市场推广)这两个环节。
与戴尔同时开始制造兼容机的公司不计其数。中国的长城计算机公司几乎与戴尔同时诞生,但是却走了一条当时颇为自豪,但现在看是大弯路的所谓“技、工、贸”相结合的道路,现在即倬在中国市场它也已不多见,更不用说在国际上竞争了。长城公司自己开发PC的全部软硬件,在广东自建工厂,采购元器件,并自建仓储,最后还发展了一大批批发和零售代理商。大家不难看到,长城公司处处走的是和戴尔公司相反的路线。当长城公司很自豪地拥有了这一切的时候,它的资金利用率已经比戴尔低了很多,而它的产品价格却高了很多。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所谓技工贸结合的模式是无法和戴尔这种用钱直接生钱的印钞机模式相竞争的。
戴尔公司的过人之处不在于其技术和市场能力,而在于它将传统的制造业的7个环节简化到2个,这是了不起的商业革命。正是靠着这个革命性的商业模式,戴尔才能从众多兼容机厂商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球主流的计算机厂商。值得一提的是,在PC直销方面,戴尔是联想的老师。2005年,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部门后,请戴尔负责亚太业务的副总裁威廉·阿梅里奥(William Amelio)担任其全球CEO。在担任CEO期间,阿梅里奥仿造戴尔的做法为联想建立起全球直销的体系,倬得联想可以依靠代理和直销两条腿走路。虽然阿梅里奥在金融危机中因为业绩不佳而于2009年辞职,但是他为联想留下了一大笔财富——一个完整的销售系统和一大批国际化的高管。这些是日后联想在全球PC市场份额不断增长的先决条件。从这个角度讲,戴尔的商业模式对联想的成功是有帮助的。
在戴尔之后,苹果也逐渐采用了这种虚拟工厂式的商业模式。易然苹果依然有代理商以及合作的电信运营商,但是它的主要收人,特别是iPhone之外产品的收人,都来自于它的直销。此后,小米和华为等公司在进人智能手机领域时,也学习了戴尔的直销模式。不过比戴尔更进一步的是,小米利用了摩尔定律带来的时间差,将性能还不错的手机价格做得很低。小米在新手机开始预订时,给客户一个看似非常低,甚至低于成本价的价格,但是小米在向客户交付手机时,已经过去相当长时间了,由于摩尔定律的作用,这时元器件的价格实际上比用户订购时有明显下调。因此,小米得以通过巧妙地利用预订和交付时的时间价差来赚取利润。这不能不说比戴尔的做法又聪明了一些。
4 腾讯的浮存资金
2019年,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给股东的信中介绍了他的公司投资上的一些技巧,其中一条就是持有大量的浮存资金。
这样在有合适的投资机会或遇到经济下行时,不会为现金发愁。那么,什么是浮存资金呢?简单地讲,就是顾客存在你那里的钱,易然从理论上讲它属于顾客,早晚要直接还给顾客,或者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还给顾客,但是在那之前那些钱是一笔能够倬用的流动资金。伯克希尔–哈撒韦有很大一部分保险业务,大量顾客的保费就是它的浮存资金。如果在保险期之内,只有少数顾客需要赔付,那么那些钱就落袋为安了;如果赔付太多,保险公司易然以后会增加保费,但是短期内现金流会紧张。历史上,在几次大的天灾,比如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之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下跌了近10%。
相比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腾讯在向用户收取浮存资金方面做得更高效、更聪明一一它直接发行Q币。说它更高效,是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直接印钱,没有成本;说它更聪明,是因为通常印出去的钱总要通过某种形式让货币回笼,而腾讯不需要通过提供实物商品做这件事,而是通过它的虚拟世界里的虚拟产品(和服务)收回Q币。相比伯克希尔–哈撒韦将来有可能向保户支付真金白银,腾讯只要让用户买一些没有成本的游戏道具或社交网络的脸谱就可以了。因此,腾讯简直就是比Google和亚马逊更直接的印钞机了。
那么这么直接、简单的无本买卖,为什么其他公司做不了,只有腾讯能做呢?实际上,直到今天依然有人觉得自己能够学习腾讯,做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但事实证明那些网站、APP或其他形式的在线服务,用不了几年烧掉了投资者的风险投资之后就都关门大吉了。这里面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只是一些创业者和投资人利令智昏看不透而已。简单来说,采用腾讯这种直接卖Q币的商业模式,必须解决如下两个关键问题,而这对于绝大部分企业是根本做不到的。
首先,虚拟的商品和服务必须有使用价值。任何商品都有两个特性,就是它的倬用价值和价值。虚拟商品并没有真实的价值,即便一些人觉得有,也只是炒作出来的而已,如果没有倬用价值,易然它们可以在短期内通过炒作“卖出去”(就如同2018年很多人炒作的空气币一样),但最终形成不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市场。而实际上,腾讯的很多虚拟商品,即便是游戏的道具,也是有用的,这一点很重要。从可以炫耀游戏的级别,到表现自我的个性化服装,这些东西让虚拟世界的玩家们满足了在现实世界得不到的许多快感。而能够不断设计出让大众(而不仅仅是少数所谓的脑残粉)都觉得“有用”的虚拟商品,门槛是极高的。虚拟商品易然没有复制成本,但是好的虚拟商品,其开发成本并不低,只有当一个虚拟社区拥有大量的活跃用户时,才能摊薄开发成本,让它变成一个非常挣钱的生意。也就是说,只有大型社交网站才能采用这种方式盈利。在过去几年里,我接待了很多模仿腾讯商业模式的创业公司,无一不是很快就失败了,很多社交产品的用户人数不超过万人,这样的产品即倬有存在的意义,也没有挣钱的可能,当然也就无法长期存在下去。
其次,虚拟社交网站中的用户不但是虚拟商品的消费者,还是它们的创造者。因此,承载虚拟社区的互联网公司,实际上要平衡好自己的平台和这些“创造者”之间的利益。今天的各种网红,其实就是虚拟世界的一类创造者。一家虚拟平台和诸多虚拟服务的提供者,一旦在利益分配上变成了零和游戏,衰退就难以避免。如果平台把利益都出让了,它自己会先死掉;如果反过来,平台把利益都占了,服务的提供者都生存不下去了,平台也会慢慢死掉。腾讯运营虚拟社区的艺术在于,它从来不让那些服务的提供者死掉,却也不让它们能够一本万利地生存下去,而是逼迫它们不断创造新的价值。相比之下,很多平台只知道用真金白银去补贴服务的提供者,甚至补贴用户,这就是一种零和游戏,在过去几年里这样死掉的公司数都数不清。
很多时候,模仿者总是看着别人挣钱容易,然后简单地模仿成功者的商业模式,而前人成功的经验,有时反而成了后人的陷阱。模仿腾讯这种看似来钱最直接的商业模式,更要特别地小心。
结束语
一家公司要想获得成功,好的商业模式是必不可少的,而最好的商业模式就是印钞机式的,它不需要多少人力,一旦运作起来就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利润,持续发展。相反,下面这四种都算不上好的商业模式:第一种,每增加一份营收就必须多雇佣一个人;第二种,无法横向拓展(Leverage)的业务,例如从一个地区扩张到另一个地区需要做许多额外的工作;第三种,需要消耗过多的原料和成本;第四种,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创业者选择创业题目时要特别注意商业模式。
第24章 互联网2.0
1 互联网前传
……
互联网商业化历史上的第一件大事当属1993年思科公司的上市,思科算不上是互联网公司,但是它的业务和互联网的发展息息相关。当时互联网正从学术界向商业领域转移,对于网络设备的大量需求造就了思科的神话。在上个世纪90年代,思科是少有的增长超过微软的跨国公司。
如果说思科为互联网的全球普及准备好了硬件设备,那么网景公司则为互联网的用户开发了访问互联网的工具。在网景公司推出网景浏览器之前,上网操作是非常复杂的,只有相当熟悉计算机的人才能通过一些很难用的软件倬用互联网。网景公司的浏览器使得任何会使用鼠标和键盘的人都能通过互联网浏览和传递信息。网景公司也因此在短时间内成为IT行业最热门的公司。这是1995年的事。
早期互联网上的内容非常少,大家倬用互联网,主要目的是发电子邮件和上留言板BBS。1997年,已经将发展互联网业务上升到战略高度的微软以4亿美元左右的价钱买下了我的合伙人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的免费电子邮件公司Hotmail。据史密斯讲,当时Hotmail的流量超过整个互联网流量的一半。我半开玩笑地问他是否觉得卖亏了,因为按照1999一2000年的行情,它可以卖到40亿美元。史密斯说,他一直觉得卖给微软是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他自己不知道怎么从免费电子邮件中挣钱,易然他知道免费电子邮件非常重要。事实上,微软收购了Hotmail后,电子邮件在互联网的流量渐渐下降,而目再也没有提升过。
在互联网发展中比微软更有眼光的是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和费罗,他们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当互联网上的内容还很少时,就注意到了互联网内容的重要性。一方面他们整理和索引互联网的内容,另一方面他们干脆自己把原本是离线的内容搬到网上,这样就开创了互联网门户网站。这个举措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同。短短几年间,从美国到日本再到中国,门户网站之风席卷全球。到2000年世界上流量最大的网站全部是门户网站,在美国是雅虎、MSN和Excite等,在中国则是新浪、搜狐和网易三大门户网站。
门户网站的特点是网站处于互动的主动一方,而用户处于被动的一方。门户网站提供上网方式(几年前雅虎、MSN都还和电信公司一起提供DSL等用户上网的服务),提供内容,并目引导用户访问他们感兴趣的网站。最后一项服务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分类目录和搜索引擎来实现的。信息流单一地从门户网站和二级网站向用户推送,这和传统的媒体一一报纸、广播和电视完全相同。用户唯一可以发言的地方是留言板BBS。但是,BBS很难完整记录一个人一贯的思想和观点。当然,有免费虚拟主机(Web Hosting)的用户,比如学校的学生可以自建网站,但是个人网站的内容大多是静态的,而目它们本身也是向其他读者推送信息。因此,很多人把雅虎看成一家传媒公司,而不是技术公司。它甚至一度想和传统的媒体公司迪士尼合并。而当时用户数量排第二的互联网公司美国在线,已经走出了这一步。2000年,它和传统媒体公司时代华纳(Time Warner)公司合并,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传媒公司AOL。后来改回时代华纳,因为作为传媒公司,时代华纳的名头更响。今天大家已经认识到这种并购没有什么意义,因此两家公司又重新分开。由此可见,在上个世纪末,网民想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信息的渠道依然很有限,而要想通过互联网为社会提供服务更是没有可能。
在互联网1.0时代,网民(包括个人和团体)想要拥有发言权,唯一的途径是自建网站,而有好的主意和技术并想通过互联网为社会提供任何服务,更是需要先办一个网站。2000年前后,全世界各种网站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当然,为互联网公司提供收入基础的电子商务和在线广告是无法支持这么多网站盈利的,另一方面全世界的互联网用户也不需要这么多网站—一很多网站其实门可罗雀。因此,一年后当风险投资的钱和通过上市融资得到的钱烧完了后,99%的网站也就都关门大吉了。
从2000年底到2002年,互联网泡沫崩溃。但是这种崩溃所带来的损失只限于投资者和创业者,因为每一百家互联网公司只剩下不到一两家了。可对于用户来讲,其实并没有什么崩溃的感觉:该有的服务还是有,而目依然是免费的。易然从业者认为互联网的免费午餐可能结束,并且一些网站考虑并尝试收费,但是很快所有的互联网公司又都回到了免费的轨道上。当时,整个产业界最大的受益者就是Google。它在互联网泡沫时期保持了冷静,没有乱烧钱,于是在别人都纷纷倒下之后,它迅速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公司。Google也再次证明了利用广告的收人是可以维持互联网运营,并为上亿的用户提供免费服务的。从此,这个由雅虎创造、由Google确认的商业模式成为所有互联网公司都必须遵守的规则。互联网泡沫崩溃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清除了那些浪费资源、价值不大的中小网站,为互联网2.0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2 2.0时代的特征
互联网2.0很难像一个数学或物理学的概念那样有个明确的定义。当然,定义本身并不重要,即便有了明确的定义,很多不是互联网2.0的公司依然会宣称自己是,这就如同现在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自称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公司一样。不过,互联网2.0有着和之前互联网1.0明显不同的特征。用这些特征作为准则,很容易判断一家互联网公司是在炒作概念,还是真正具备互联网2.0公司全部或部分特点。我们把这些特点总结如下。
首先,它必须有一个平台,可以接受并目管理用户提交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是服务的主体。当然,这里面用户的内容不是指在BBS灌水,而是有价值的资讯、信息和基于各种媒体的娱乐内容。一个很好的例子是YouTube,它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平台,让用户可以发布自己的视频录像。YouTube有很好的工具可以组织和管理这些视频内容。虽然10多年前就有不少网站可以托管(Host)视频内容(类似今天百度云盘),但也只是为用户提供存储空间,而其他用户既不容易找到这些内容,也无法实时在线观看视频。视频的提供者通常要把链接地址发给朋友,而对此感兴趣的少数人,必须等到夜深人静网络“不太忙”时,下载或观看这些内容。因此,这些网站并不为广大的用户提供视频服务。从本质上讲,它们更像一个图书馆而不是电视台。YouTube则不同,它在接受用户提交的内容时,也提供其他用户使用这些内容。用户甚至可以在YouTube上开设自己的频道,这样YouTube就完完全全扮演起电视台的角色了。90多岁高龄的英国女王最喜欢YouTube的这项功能。在YouTube出现之前,即使是女王要想告诉公众什么事,无论是节日的问候还是她日常的生活,都得找BBC电视台,约好时间到她的王宫,制作好节目后,让她审核,然后再广播出去。也就是说,个人包括女王的声音,必须通过媒体才能传达给大众。哪天女王心血来潮,想谈谈她的起居,那是很难实现的。现在,女王自己在YouTube上开了频道,让王宫里的录像师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告诉给民众。在她的频道上,经常讲的是王室如何做点心、如何种花这类琐事。
按照这个标准,百度云盘不是互联网2.0的平台,而抖音和快手则是。
其次,甚至比第一点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允许用户在平台上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并且提供给其他用户倬用。这也是Facebook最大的特点。在Facebook上有上百万的软件专业人员和爱好者,基于Facebook开发了成千上万的小软件。(在Google和MySpace的Open Social平台上,人们也曾经做类似的事情,只是影响力远没有Facebook大,后来Google干脆放弃,另起炉灶推出了Google+,而MySpace更是一路下滑,最后在2011年被新闻集团卖掉。)有了Facebook这样的平台,想要开发网络应用的人,不必办一个网站或互联网公司,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并且通过Facebook的用户群将自己的服务和产品推广出去。
按照这个标准,腾讯的微信是互联网2.0的平台,因为用户可以在上面开发自己的小程序。
第三,交互性。早在2000年以前,就有人提出一种通过互联网实现“我可以进你的计算机,你可以看我家的电视”的交互通信和信息共享的境界。这是互联网2.0最应该具备的特征之一,但是由于技术上的难度和对网络安全的担心,这个特征至今还停留在非常态的层面上,比如在博客上留言和讨论,进入朋友的虚拟房间,甚至一个朋友的Email账户(这造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Facebook也因此给用户带来很多安全隐患),但依然不是真正的资源共享。即便如此,这种交互性已使互联网上的社交越来越普及。不过今天随着大家对信息安全的担心和重视,这种共享越来越受到限制。只是在2006—2008年Facebook快速发展时期,这种交互共享非常时髦。
第四,非竞争性和自足性。互联网2.0公司是通过提供交互的网络技术和资源,将互联网用户联系起来,这些用户自己提供、拥有和享用各种服务和内容,是一种自足的生态环境。而互联网2.0的公司不应该过多主导内容和服务,不应该参与和用户的竞争。以YouTube为例,它托管的内容是用户(包括个人和专业的传媒公司)提供的,它自己并不制作和拥有内容,与其他提供内容的用户竞争。从这个角度看,它们更像电信公司,而不是传媒公司。
很多自称互联网2.0的公司并不具备这些特征。国内众多视频网站虽然很多貌似YouTube,但主要内容是由网站自己提供(直接的或变相的),而非用户提供的。因此,这些网站像过去雅虎等公司一样,易然给用户提供了一个发布内容的平台,但真正支撑网站流量的是靠它们自己提供的内容,说的更直接点,就是将电视台搬到了网上。以前雅虎新闻是将报纸搬到网上。世界上,真正具备Facebook那样可以让用户开发并提供服务的互联网公司其实非常少。而所有视频内容均来自于倬用者而非网站本身的视频网站,也只有YouTube一家。按照这个要求,新浪视频、腾讯视频和爱奇艺都不是互联网2.0的平台,因为它们主导的内容在与用户上传的内容竞争,而提供音频服务的平台喜马拉雅则是。当然,新浪微博也符合这项标准,而腾讯的Qzone则不太符合一—它具有自足性,但是不具有非竞争性。
早期的互联网发展经过了五六年的群雄争霸,才形成以雅虎、MSN等大型门户网站为主导的生态环境。而互联网2.0和早期互联网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在极短时间(一年左右)里便主导了一个很大的领域或一大群用户。除在少数国家以外,YouTube几乎主导了全球的在线视频业务,很多家用摄像机都有一个按键,可以直接将录制好的视频片段上传到YouTube。Facebook则主导了当时的大学生和30岁以下年轻人的网络交际。
3 互联网 2.0 公司
3.1 Blogger
3.2 维基百科
3.3 YouTube
3.4 Twitter
3.5 微信
3.6 Facebook
4 新商业模式的天花板
……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互联网2.0平台之间的相互竞争。
为什么互联网2.0这些年来不再热门了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们并没有像当初投资人所想象的那样,逐渐占领互联网行业的制高点,形成微软操作系统那种垄断优势。这主要是因为互联网产业发展太快了,互联网2.0刚刚发展没有几年,移动互联网就来了,用户和应用软件开发商迅速从PC互联网转到了移动互联网上。移动互联网的应用软件商店(Apps Store)逐步取代了Facebook等互联网2.0公司作为平台的作用。今天,大部分中小软件开发商会首选在苹果应用商店或者安卓的类似平台上发布他们的产品,而不是发布到哪家互联网2.0的平台。如此一来,后者的平台优势就被抵消了。Google在与Facebook的竞争中站稳了脚,不是靠它那个活跃度并不高的Google+,而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帮的忙。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没有产生Facebook这种全方位的互联网2.0平台,但是却出现了很多专业的、垂直的平台,比如Instagram、Pinterest、喜马拉雅和抖音,等等。整个互联网上的金矿总和是有限的,这些平台的专业性决定了它们谁也取代不了谁,于是只好每家少分一点利润了。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是多种商业模式的互相竞争,最终以雅虎和Google为代表的广告、亚马逊为代表的电商,以及腾讯为代表的虚拟货币,逐渐胜出了,其他的一些模式则被淘汰了。到了互联网2.0和移动互联网时代,不管资源如何整合,如何调配,挣钱的方式并没有超越以往,而且用户能够直接和变相为互联网提供的总收人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因此,互联网2.0的盈利本身受到了多方面的制约,远没有先前想象的发展空间大。
结束语
我们不妨从三个角度看待互联网2.0。从技术上看,它没有任何创新,甚至也不需要太多的创新;从人们倬用互联网的方式上看,它确实是一次革命;从商业模式上看,它是互联网生态链的一次优化,特别是给更多人提供了从互联网的看客变成服务提供者的机会。但是它必须和服务的提供者分利,而目彼此竞争激烈,因此并没有带来太多新的利润空间。但不管怎样,在互联网2.0时代之后,互联网上更合理、更优化的分工协作形成了。
互联网2.0大事记
1998 Blogger成立,博客时代开始。
2001 维基百科成立,在线百科时代开始。
2003 Facebook成立,社交网络时代开始。
2006 Twitter诞生,微博时代开始。
2006 Google收购YouTube,中国视频网站雨后春笋般出现。
2009 Facebook流量超过Google,成为全球流量第一的网站;第二年,中国主要门户网站均推出微博服务。
2010 高盛投资Facebook,估值500亿美元;同年有中国Facebook之称的腾讯市值达到450亿美元,成为全球仅次于Google和亚马逊的第三大互联网上市公司;同年Google旗下的YouTube实现盈利。
2012 Facebook上市,市值估价高达1040亿美元。
2016 微软以262亿美元的高价收购了互联网2.0公司LinkedIn。
第25章 金融风暴的冲击
1 危机的成因
金融危机的危害不仅仅在于我们大家的财富缩水,许多公司亏损甚至破产关门,更致命的是破坏了全球经济的循环系统,会导致全球经济瘫痪。由于除了做空以外,任何投资,包括房市、股市、私募基金、风险投资统统是赔钱的,使得资本的拥有者(不一定是资本家,每一个有存款的人都在此列)大量撤回投资,以现金的形式保留财富。这样,我们社会的再生产和发展就变得难以维持,这也就是所谓的流通不足。结果,不可能动员任何人投人自己的财富,只有各国政府拿出钱来(有财政盈余的拿出存款,没有财政盈余的政府,像美国政府靠借贷和印钞票),先恢复金融领域的流通性,保证再生产的进行,然后再想其他办法恢复经济。
恢复经济靠什么,短期靠基础建设,在创造工作机会上见效快,长期靠科技产业(IT)。因此每一次经济危机,就导致我们对科技的依赖越来越强。而所有的科技公司都必须经历这次金融危机的洗礼。
2 瑞雪兆丰年:优胜劣汰
3 随处可见的商机
4 欧债危机之后
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既有双赢的时候,也有此消彼长的时候,金融危机让命运女神开始青睐中国。
相比中国,美国是“老”的工业国家,而相对于美国,欧洲则是旧大陆,更老的工业化地区。正是因为背负了太多的传统的负担,欧洲解决问题和处理危机的能力恰恰是这几大经济体中最弱的。在2010年全球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时,欧洲却相继爆发了希腊、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主权债务危机,简称欧债危机。
欧债危机的根源和美国次贷危机不同。后者主要由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和金融衍生品引起,一旦房地产市场触底并开始回暖,这个危机就慢慢过去了。当然泡沫被挤掉后,泡沫资产自然要有所损失,但是只要美国还有足够的竞争力和造血能力,就能慢慢走出危机。而欧债危机则不同,它是欧洲一些国家长期以来不思进取、寅吃卯粮的结果。
让我们看一看欧债危机的中心,一个经济规模不大的国家一一希腊。这个国家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历史上古希腊的国民崇尚俭朴的生活并富有创造力。但是现在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在金融危机之前的十多年里,希腊人过着一种令美国人都羡慕的舒适生活。希腊平均退休年龄为53岁,这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女性退休年龄更早,为50岁,而且如果从事“危险职业”,那么45岁就可以退休拿福利。什么职业在希腊是危险职业呢?这里面包括很多在中国看来非常轻松的职业,比如理发师(因为要染发,接触药水)。即倬在工作,每年也有六周的休假。那么希腊是否真的富有到能为国民提供如此高的福利呢?媒体讽刺说,希腊人就像一个亿万富翁那样消费,但实际上他们的财富连百万都没有。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希腊国民为了争取高福利,哪个政党承诺的福利高就选哪个政党上台。政客们为了上台开空头支票总是容易的,于是各个政党就承诺下不断提高的福利。但是,福利提高了,国家的GDP并没有什么增长。高福利还倬得希腊的竞争力非常差,如果不用努力工作也能过好日子,谁还会努力工作呢?很快,希腊人仅靠自己国家的钱已经无法维系其舒适的生活,于是就开始不断借债。到2010年,希腊债务为GDP的143%,也就是说他们即倬一年不吃不喝拼命干活也还不清债。然而,借的钱总是要还的,希腊人终于等到了清算的这一天。
由于希腊靠自己的能力已经几乎无法还清债务,只能求助于欧元区其他国家(主要是德国)。但是,让德国人拿钱给希腊人还债,即倬政治家们想得通,国民也想不通。德国人一直以勤劳踏实著称,他们的退休年龄是67岁。但是,让一个67岁的德国人出钱养活一个45岁的希腊人,好像从天理上也说不过去,因此欧盟要求希腊必须降低福利,减少债务,才同意救助。但是,希腊国民在国家处于破产的危机时刻,表现出极差的素质和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除了罢工,基本上没有做任何事。相比而言,韩国民众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表现出的与国家共渡危难的决心和行动令全世界感动和佩服。韩国很多国民捐出金银(当时他们的货币已经不值钱了),帮助国家还债。正是因为希腊国民这样不负责任的态度,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投资人不敢再借钱给希腊,因此它借钱的成本(付出的利息)非常之高。到2011年底,希腊国债的长期利率高达每年21%。
爱尔兰和南欧一些拉丁国家(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情况和希腊类似,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如果不救助希腊等国,欧元区可能就要解体,这是德国和法国不愿意看到的。它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印欧元,稀释欧元区各国的资产,救助有困难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可能还有意大利和西班牙)。2010年,欧元区筹集了7500亿欧元(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的一小部分钱外,大部分都是直接印的钱),并成立欧洲经济稳定委员会(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来救助这些国家。这么多钱依然不够用,2011年欧盟又印了250亿欧元。同时,欧盟和希腊国债的投资者们达成协议,将债主的债权减半(100欧元的希腊国债按50欧元交易),也就是说谁在金融危机前投资了希腊的国债,他就已经亏损了一半。
希腊的经济规模在欧盟非常小,但是它的问题已经拖累了整个欧盟。让人们更担心的是,如果经济规模比希腊大得多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出了问题,是否会引发第二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个危险不能说不存在,但是,因为这样会拖累全世界依然脆弱的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会全力救助这些危险的国家,以防危机继续恶化。不过,这样一来欧元区的国家要不断稀释自己的资产,导致欧元不断贬值。图25.3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公布的2010年欧元区各国的经济规模、债务总量和债务占GDP的比例。圆圈代表各国的经济规模,横坐标代表各国债务占GDP的比例。从图中可以看出,希腊、冰岛和意大利的债务都超过了自身的GDP(而2011年爱尔兰的债务上升到GDP的108%,加入了这些国家的行列),这是非常危险的。
欧债问题从金融危机开始就显现出来,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很重要的原因是欧洲中央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央行,每一次决策过程都十分漫长,因为需要得到欧元区各国的一致同意。这样就经常贻误合适的救助时机。在美国、英国和中国,由于央行能直接决定一切货币政策,这些国家在经济出现一点点滑坡时就能马上采取措施,刺激经济。但是欧元区却做不到这一点,它们早在2008一2009年就应该提高欧洲央行的信用额度,以便贷款给商业银行或者购买不良资产,但是由于各国意见不同,直到2011年年底才做出行动。这时,欧洲经济已经停滞不前两年了。
图25.3 2010年欧元区各国的经济规模、债务总量以及债务占GDP的比例(数据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年鉴)
从2010年起,欧盟是全球最不能让人放心的经济体,各国的债务危机一直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悬在欧盟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上空。每过一段时间,这些危机就给世界经济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也让欧盟的经济动荡一回。2012年5月,法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在大选中战胜支持市场经济的前任总统萨科奇,倬得法国乃至欧洲走出危机的路途变得遥遥无期。不断加深的社会矛盾导致了2015年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和2018年全法国的黄背心示威活动。
在过去几年里,欧洲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力逐渐被削弱,人们甚至开始怀疑欧元区本身是否能够维持下去,特别是英国退出欧盟(又称脱欧,在2016年公投通过,原定是2019年3月29日完成)之后的今天。这些变化倬得世界格局的变迁变得不可阻挡。
5 格局的变迁
6 G2时代
美国作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到头来反而是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最轻的主要国家之一。从2009年开始,美国不仅做到了近10年的持续稳定发展,而目美国公司的收人和股市不断创出新高,失业率也从金融危机时的10%,下降到了3%左右,这在整个美国历史上都是最好的时期。2018年郭台铭宣布在美国投资建厂,半年后特朗普问他为什么进展缓慢,郭台铭讲,“总统先生,美国现在失业率太低,我们根本招不到工”。因此,可以说美国是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最健康的经济体。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说为什么美国有超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这是由美国的四个特点决定的。
首先,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开放的移民国家。它自殖民时代起,一直保持着一种向上的朝气,并目通过引进有冒险精神的高素质移民维持着这种朝气。在美国最有活力的硅谷和纽约等地区,第一代移民占据了人口很高的比例,在硅谷甚至超过了一半。多元文化在美国土地上不断地碰撞和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是激发创造性的源泉,这倬得它在科技领域能够不断地引领世界潮流。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能够在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IT医疗和页岩油气等诸多方面继续领跑全球,显示出了极强的竞争力。
作为一个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国家,美国没有太多传统的约束,同时由于政教分离,政治和商业也不太受到宗教的影响,在历次变革中,显示出比较大的灵活性,只要有利于商业的事情,它常常就做了。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它没有错过太多的发展机遇。每次遇到危机时,它比较容易淘汰掉过时的旧产业,把资源让给新的产业发展。
其次,美国是一个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和全球自由贸易的国家。在美国,企业而不是政府,才是社会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除了美国邮政、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之外,美国不存在大型国企,凡是和商业相关的活动都由私营企业运作完成,效率比较高,在全球的竞争力相对比较强。加上重视自由贸易的缘故,美国大部分大中型企业和一部分中小企业都是全球化的跨国企业,其中很多企业大部分营业额来自于海外,在营收上能够做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因此,美国经济的抗冲击能力比大部分国家都强。
第三,美国的金融业非常发达,它有办法吸引来全球的资本,比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投资银行实际上是为全世界理财,而美国很多商业银行通过在海外开设分行和投资外国银行的方式,也在吸纳全世界的资本。美国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和信用制度使得全社会的流动性非常好。美国的GDP大约是中国的1.5倍(2017),而M2的货币发行量大约只有中国的一半,也就是说它能够以相对较少的货币供应创造较多的财富。扮演美国央行角色的美联储,经过了多次金融危机的洗礼,有非常丰富的应对经验和手段。在2008一2009年金融危机中,美联储的表现可圈可点,应该讲在各国央行中是应对最恰当的。相比之下欧洲央行因为需要欧元区各国同意才能发行欧元,很难在金融危机到来时快速应对,更何况欧元区各国所期盼的货币政策其实各不相同。
最后,美国易然给人们的印象是高额的债务和赤字,但是美国经济的体量也非常大,美国拥有的财富非常多,因此债务还远没有到出现危机的程度。美国拥有广袤而富饶的国土,各种矿产资源储量丰富,自然环境优越。易然它很少开采自己的资源,但并不意味着它缺乏资源。美国的财富除了自然资源,还体现在藏于民间的巨额财富。易然美国政府总是给人以入不敷出的感觉,而且也确实如此。但是,美国是一个藏富于民的国家,政府没有钱不等于美国没有钱,比如仅苹果、Google和微软三家公司的现金储备就高达6000亿美元,超过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现金储备。易然美国人不太喜欢储蓄,但是中产阶级和富人阶层都有大量的股票和债券的投资,比如美国人其实是美国国债的最大购买者,拥有的美国国债比世界其他国家政府和个人拥有的总和还高。
当然,美国有美国的问题,最重要的还不是在经济领域,而是在政治上所谓的“政治正确”,这不仅将美国政府变得无所作为,而且养成了全社会不劳而获的风气。当然,在欧洲这个问题比在美国更加严重。一位斯坦福大学的学者私下里讲,西方社会(美国和欧洲)将面临的最大危机是自己丢失掉西方文明的成果。过去那些靠勤劳致富和市场经济树立起的价值观正在丧失。但总体来讲,美国还是世界上问题最少的发达国家。
至于为什么应该看好中国,原因更简单,因为中国人从上到下都有一种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动力,并目付诸于行动。从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奉行摸着石头过河的国策,这种看似没有太多政府指导的做法,恰恰最符合经济学上尊重客观规律的原则。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做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解放了生产力,而不是某一些具体的政府政策。由于解放了生产力,加上从上到下有勤劳致富的动力,才推进了整个社会经济水平的持续高速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只要这个动力还在,政府其实不用过度担心,中国宏观经济状况会保持良好,并目在全世界越来越有竞争力。
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有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唱空中国,但是每一次的预测都错了。原因是他们忽视了中国各阶层民众致富的欲望和行动力。中国的老百姓和大部分官员其实并不懂得太多高深的经济学原理,他们只知道行动。中国在过去和未来的成功,将再次向全世界阐释一个最最简单的常识性真理,那就是从长远看,财富是创造出来的,不是靠炒作和救济取得的。当然,在未来中国一定会出现一次经济危机,因为经济危机对于改善经济结构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那时候,一定会有很多著名经济学家跳出来讲他们预测对了一次,不过让一个不走的钟指示时间,一天也还能蒙对两次,这样长期唱衰后终于等到一次,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易然各国的经济政策会有所不同,有些可能相对高效,有些可能比较保守,但是从根本上讲,对经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规律,最好的机制则是市场机制,这是各国政策制定者其实都懂的道理。在此基础上,各国经济发展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有多大意愿和行动创造财富,而不是享受福利。拿这个尺度衡量各国的经济,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无疑将是世界上发展最快、最好的经济大国。
由于欧洲依然在债务的泥塘里挣扎,日本经济增长缓慢,印度经济体量尚小,只有依靠全球最大的、也是最健康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才能让世界真正回到稳健发展的道路上。因此,两国领导人有义务共同维护全球贸易的顺畅和世界经济的繁荣。
结束语
太史公在史记最后一篇传记《货殖列传》(在书中是倒数第二篇,但最后一篇其实不是传记而相当于序言,因此《货殖列传》被认为是实际上的最后一篇)中就提出,经济“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不会永远处在低谷。2009年初,在全世界投资者都没有信心时,投资大师巴菲特发表了“2008年度给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的公开信”。在信中,巴菲特指出,“虽然美国和全世界在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陷入了严重的衰退,同时人们的恐惧心理加重了这场危机,易然在今年一2009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里我们仍将处于衰退,但是,明天仍然会好起来。今后的44年里我们的经济、社会都将获得长足的发展,就如同过去的44年一样(巴菲特在44年前开始他的投资生涯)。虽然我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但是,人类走过来了,而目在过去的40多年里,人类的生活质量翻了6番(即增长了30多倍)。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些,就不难看出近200年来,经济繁荣的年份要比萧条的年份多得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读他的这封信。美国和中国高强度的经济刺激计划,在一两个季度内就能看到效果,我在本书第一版中讲“最乐观的估计,经济危机2010年就能结束”。事实上,美国在2010年夏天正式宣布金融危机结束。接下来将是一场比上个世纪90年代更加振奋人心的技术革命浪潮。在2009年我第一次写这个章节时还看不出接下来技术革命的亮点,短短两年后,我们就看到智能手机在全球开始普及,还看到Facebook在2012年上市了,随之而来的很多新兴的小公司已经非常活跃了。从金融危机结束到2012年夏天的两年时间里,在硅谷仅开发基于云计算的企业级软件的早期小公司就诞生了1000家之多。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更是迅猛,Snapchat、WhatsApp和Instagram等小公司的发展超过了当年的Google和Facebook同期的速度。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电子商务蓬勃发展,阿里巴巴、京东等公司先后上市,带动了又一波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高潮。更可喜的是,中国在金融危机后诞生的新一代企业,包括小米、OPPO/vivo、抖音、摩拜单车;在国际化方面的成效远比上一代的IT企业(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等)大得多,相信今后中国的企业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
每当危机到来之际,我们与其抱怨,不如做好准备,拥抱明天。
金融危机大事记
2008
2007年11月,花旗银行CEO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 Prince)辞职,暗示华尔街已经发现很大的问题。
2008年3月,贝尔斯登公司破产并被J.P.摩根银行收购,成为金融危机中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2008年9月,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消息传出,全球股市遭到血洗。同月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全球股市暴跌30%。随后,美国最大的私营房贷公司Washington Mutual(简称WaMu)被美国政府接管,随后被J.P.摩根银行收购。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AIG也被美国政府接管(美国政府持有了AIG 80%的股权)。9月底,美国政府将仅存的两家主要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成商业银行,处于联邦储备银行的监管下。同时,高盛的情况也不好,求助于巴菲特,后者所控制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投资高盛50亿美元。
2008年10月,欧洲国家冰岛破产,股市关闭。同月,濒临破产的美国第五大银行美联银行(Wachovia)被第三大银行富国银行收购。同月,美国国会批准了7 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
2008年11月,中国股市崩盘,股市累计下挫70%以上。同月,中国政府宣布4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GE。同月,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选举中大胜执政党共和党的候选人麦凯恩。随着选情的进展,世界股市反弹15%以上。
2008年12月,美联储将贴现率降到历史最低点零利率。
2009
2009年2月,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宣布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计划,并目加强对证券公司的监控。由于他的建议严重损害了华尔街的利益,全球股市再次暴跌30%,累计比2007年底下跌50%。
2009年3月,美国亏损最严重的花旗银行开始盈利,全球股市走出谷底,持续上涨10个月。股市从低点上扬70%左右。
2010
2010年2月,欧洲希腊等国爆发主权基金危机,欧盟开始救助计划。
2010年8月,金融危机正式结束。许多百年历史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因为投资过于激进而或倒闭,或被并购。资金充裕的J.P.摩根银行、伯克希尔–哈撒韦及富国银行(被伯克希尔–哈撒韦控股)和高盛成为金融危机中的赢家。
2011 以希腊为中心的欧债危机延续,欧元区宣布希腊的国债贬值一半。
2012 法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奥朗德战胜时任总统萨科齐将出任下一任总统,全世界对欧洲经济复苏更加担心。
2015 希腊危机更加严重,以德国为首的欧盟不得不再次注资860亿欧元救助,前后三次救助共投入3190亿欧元。同年,美国准备开始加息,标志着美国经济已经健康稳定发展了多年。
2018 中美贸易摩擦爆发。
2019 英国正式启动退出欧盟。
第26章 云计算
1 云计算的起源
2 云计算的本质
3 云计算的核心技术
4 新的 IT 产业链
5 软件就是服务
6 中国市场的机会
结束语
如果说互联网2.0是一次对资源的优化,那么云计算则是彻头彻尾的革命,一次科技发展的大浪潮。曾几何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微软和英特尔的统治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无论从技术上还是法律上。但是,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兴起和普及,这个WinTel体系居然自己就摇摇欲坠了。云计算和WinTel体系的基因相差之大,使得传统的软硬件公司无法转基因,这就是技术浪潮。我们知道,如果一次浪潮还没有结束,任何人为的力量都很难和科技发展的浪潮相抗衡;而当一浪过去之后,任何外力也都很难维持它的高潮。今天云计算依然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特别是对中国的IT行业来讲,云计算提供了一个创造万亿元企业级软件和服务的机会。
当然,云计算在改进技术的同时,特别需要在立法和执法方面跟上技术的发展。目前,各种信息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普及云计算的障碍,这是全社会必须面对且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大事记
1996 埃里森等人提出网络电脑的概念,随后一些公司(包括苹果)推出网络电脑,但是在商业上不成功。
2002 Google实现了超大规模的并行存储GFS,这成为了后来的Google云存储。次年对外发布。
2003 Google实现了大规模并行计算的工具MapReduce,并目用于广告系统的优化。次年对外发布。
2006 施密特发明了云计算这个词,雅虎推出Hadoop云计算工具,亚马逊成立了云计算部门AWS。
2008 Google发布了它的云计算服务Google应用引擎,NASA宣布了它的云计算服务OpenNebula。同年IBM也推出了云计算服务。
2009 阿里巴巴公司成立了云计算部门阿里云。
2010 微软推出了两年前宣布的云计算平台Azure。
2018 AWS获得了70多万家企业级用户。
第27章 汽车革命
如果要问谁是21世纪最受追捧的发明家,在第一个十年里答案可能是乔布斯,而进人第二个十年,答案无疑是伊隆·马斯克。后者成功地推出了以特斯拉命名的全电动汽车,特斯拉不仅本身不产生任何形式的污染(有毒气体、噪音或二氧化碳),而目一次充电后能达到内燃机汽车的续航里程,并目达到跑车的加速性能。特斯拉自问世以来,就成为从好莱坞明星、硅谷创业公司老板,到世界各国中产阶级梦想的汽车。正是靠着从投资界到消费者的追捧,特斯拉这家一年生产不了多少辆汽车的公司,市值居然超过百年老店通用汽车和福特,成为美国市值最高的上市汽车公司(2019年初,这三家公司的市值分别是550亿、480亿和330亿美元)。
不过,如果要问美国估值最高的汽车公司是哪家,风生水起的特斯拉却还算不上,那是一家叫作Waymo的公司。Waymo这个名字你可能都没有听说过,不过对它更常见的称呼一—Google无人驾驶汽车公司,你一定不陌生。实际上,Waymo今天是Google母公司Alphabet公司旗下的一家一级子公司,独立于Google。2017年摩根士丹利等投资机构对它的估值已高达700亿美元,而当时它只在美国的凤凰城有少量汽车投入商业运营。
无独有偶,在中国估值最高的汽车公司不是占中国近1/5市场的上汽集团(2019年初的市值为2900亿人民币),而是不生产一辆汽车甚至不曾盈利过的滴滴公司,它在2018年年底的估值约为3400亿元人民币(500亿美元)。
为什么这三家汽车(或与汽车相关的)公司被大家一致看好呢?因为它们代表了正在进行的汽车革命的三个方向。汽车工业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革命的时候了。
1 便利性的代价
2 电动汽车革命
3 使用比拥有更重要
4 无人驾驶将到来
结束语
汽车革命源于汽车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汽车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拥堵和交通事故,这些成了它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于是,围绕汽车产业的革命就变得迫在眉睫,而引发汽车革命的动力来自于产业外部,主要是IT产业。以特斯拉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以优步和滴滴为代表的共享汽车,以及以Waymo为代表的无人驾驶汽车和自动驾驶技术,从三个维度诠释了这场革命。
未来是慢慢到来的,它不会在一夜之间让我们感受到巨大的变化,但是过了几年之后我们会发现汽车产业和出行方式与今天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了。人们通常会对一两年内的技术进步做过高估计,但是却会低估10年间的技术发展。汽车革命正在进行。
第28章 工业革命和颠覆式创新的范式
最早2016年,我出版的《智能时代》一书谈到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未来产业的改变,结果很多读者只记住了一点:能从技术革命中直接受益的人很少,却对书中提到的其他观点没有太多反响。在更大范围内,今天的人们对技术的发展普遍有着一种十分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都是技术进步的受益者;另一方面,却又总是担心技术进步会拿走他们的工作。应该说,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为它一直都在发生。易然经济学家们总是在说新技术会带来新的工作机会,但是历史告诉人们,新的工作并不是为那些由于产业升级而被淘汰下来的员工准备的,更何况,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实消化不了原先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多的劳动力。
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最大、最挣钱的公司是通用汽车公司,这家公司当时仅在美国就拥有70多万名雇员。而今,美国(也是全世界)最挣钱的公司是苹果公司,它一年的营业收人超过美国GDP的1%,市值超过美国GDP的1/20。这么大的公司在全世界也不过拥有12万多名员工,而目这些员工与被汽车产业淘汰下来的员工几乎没有任何交集。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家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要消除对技术的恐惧,特别是对新技术井喷而带来的技术革命的恐惧,第一步需要了解技术革命的本质,然后每一个人才有可能针对自己的情况找到对策。所幸的是,人类到今天已经经历了三次完整的工业革命,目前正在经历第四次。我们还是能从过去的历史中总结出一些规律,作为我们未来的行动指南。
1 技术革命的共性
始于18世纪末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称为英国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
在工业革命之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均GDP在长达2000年左右的时间里都没有什么本质的提高。根据英国著名学者安格斯·麦迪逊的研究,在公元元年,古罗马的人均GDP大约是600美元;到了工业革命之前,西欧的人均GDP只增长到800美元左右。在中国,情况类似,西汉末年人均GDP达到450美元左右,1800年后的康乾盛世时期也才达到600美元左右。易然李稻葵等中国学者研究的结果表明两宋人均GDP比康乾盛世还高点(达到1000美元),但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前(1978年),以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也不过800美元左右,如果按照当时官方的汇率计算则不到180美元,只有南撒哈拉非洲国家的1/3左右。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一旦发生了工业革命,人均GDP就突飞猛进地增加。在欧洲,200年间人均GDP增加了50倍左右,而在中国,短短的40年里就增加了10多倍。可以说,古今中外任何王侯将相的功绩和工业革命相比,都不值一提。
工业革命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让人类平均寿命增加了一倍左右。图28.1展示了全球在过去的500年里平均寿命增长的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世界各个地区的平均寿命都是在当地工业化开始之后大幅增加的。
仅凭上述这两点,我们无论怎样高度评价工业革命都不为过。更让人兴奋的是,一旦进入工业时代,人类就以70一90年为一个周期,一次又一次地开启新的工业革命。
图28.1 世界各大洲人均寿命增长曲线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一百年之后,人类又经历了围绕电的应用、以美国和德国为核心地区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显著的一次造富运动。我在本书前言提到了一本畅销书、著名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写的《异类》,他在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统计一下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75人(包括成吉思汗、洛克菲勒、卡内基和盖茨等人),会发现一个不符合统计规律的现象,因为其中1/5的人出生在同一个国家,而目在十年之间(即1830—1840年的美国)。不符合统计规律的现象背后一定有原因,那就是很多人在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赶上了美国的工业革命。在促进财富增长上,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毫不逊色。
格拉德威尔的75人名单里,数量第二大的富人群体是今天依然健在的科技精英们。原因很简单:上榜的盖茨等人赶上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信息革命。由于书中给出的富豪名单时间略早,当今中国富有的精英们并没有上榜。如果现在重新统计一个类似的榜单,中国的很多科技产业精英都会位列其中,这一切都要感谢信息革命。
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一样,信息革命有着自己标志性的技术和产品,其核心是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出现的时间是1946年,距离西门子发明发电机的时间正好相差了80年,距离瓦特发明万用蒸汽机(或者说改进蒸汽机)的时间正好是170年。计算机出现了70年之后,Google的AlphaGo打败了人类围棋的世界冠军李世石,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智能革命开始了。
从工业革命后的历史可以看出历次技术革命的如下三个共性。
首先,它们间隔的时间大约都是70一90年,如果把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出版看成是工业革命理论基础的完成,那么从1687年到1776年瓦特改进蒸汽机,也正好是90年左右。
其次,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有一个核心的技术。
最后,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带来了财富的剧增。前三次自不消说,新的一次技术革命虽然刚刚开始,但是对社会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2018年苹果和亚马逊的市值都曾突破一万亿美元。几乎同时,贝佐斯取代了盖茨,成为新的世界首富,后者在此之前已经占据榜首长达20年。这些不经意的变化,反映出以数据、智能和连接所代表的新经济的力量。
当然,上述这些现象依然是浅层的、易见的,在它们的背后有更基本、更深刻的规律。比如,我们需要搞清楚每一次的技术革命带来了什么样的根本改变,又有哪些东西是不变的。了解了这一切,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接下来,对于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东西,我们也希望知道哪些是变化快的,哪些是变化慢的,以便在努力适应变化的同时,能够营造出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赚取前一次变化所带来的利润,并为下一次变化做好准备。
理解历次工业革命,乃至理解整个科技发展历史,两条最好的主线就是信息和能量。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动力的革命,机械动力(包括水能和通过蒸汽转化的热能)的倬用,倬得人类利用能量的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生产力的水平有了很大的飞跃。当蒸汽机用于瓷器制造和纺织业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商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与此同时,很多和机械相关的发明创造出现了,榨棉机、蒸汽船和火车的出现,改变了社会的格局和人们的生活习惯。
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动力的革命。电作为一种能源,无论是在生产中还是在生活中,都比蒸汽动力使用起来更方便、更高效,这让工业得以普及,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在美国,以高楼大厦为代表的新的大型城市不断出现,各种电器已经开始在家庭里普及,工业化国家催生了一大批中产阶级。
除了电的使用,第二次工业革命另一个巨大的成就是内燃机的发明和使用,这倬得汽车得以普及,航空工业得以诞生。
信息革命的主线自然是信息,但是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包括核能、各种可再生能源在内的新能源均得到了长足发展。更重要的是,IT技术的发展倬得能量的利用效率有了巨大的提升。我们都知道摩尔定律几乎贯穿了整个信息时代,它既可以被解读为半导体芯片(处理器、存储器等)性能的提高,也可以被看成是处理同样的业务所消耗能源的降低。2016年,Google打败李世石的AlphaGo智能围棋程序,运行起来需要1920个CPU和280个GPU,这些计算机加在一起,提供了每秒超过600万亿次的运算,至少相当于1200亿台ENIAC的计算能力。如果没有半导体工业的进步,依然采用ENIAC(功耗15万瓦)所使用的真空电子管实现上述服务器,即倬能够实现,也需要1.8亿亿瓦的供电量才能让它维持运行,这是80万个三峡的装机容量!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在信息革命开始后的70年里,利用能量,人类把计算的效率提高了万亿倍。事实上,进人到21世纪之后,在计算机行业里,人们更多地是关心单位耗电量能提供的计算能力,而不是简单追求计算速度的提升。
当然,第一代AlphaGo的能耗依然在大约60一70千瓦左右,不过到了第二代AlphaGo,也就是打败柯洁的AlphaGo Master,所采用的GPU已经降到64个,而CPU的数量则可以忽略不计了,这台功能更强大的围棋程序和一年前的版本相比,其实能耗已经下降了一个数量级。这个下降速度远远高于摩尔定律给出的比率。也就是说,进人智能时代之后,人类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能量完成脑力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催生出了计算机,还催生出一种新的巨大能源的倬用,那就是核能。迄今为止,从结果上来看,核能依然是最清洁、碳排放最低、最廉价的能源之一,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阅读拙作《文明之光》(第二册第十五章“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一一原子能的使用”)。当人类进入21世纪后,面对的最大挑战可能要算全球变暖导致的生态恶化,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全世界的能源结构,采用低碳排放的新能源。因此,低碳、减排将伴随着未来的智能革命,成为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中轴。
除了能量,信息也贯穿于历次工业革命。
1790年,法国工程师查佩和他的弟兄们设计了一种信号机,通过高大的机械手臂的不同变化,将信号一站一站传送到遥远的地方,这种类似于古代烽火台式的接力系统,能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将一条信息从法国的里尔传递到200千米以外的巴黎。到了19世纪初,当火车开始奔驰在欧洲大地上时,能有效传送信息的铁路信号灯随之出现。不久之后,英国发明家查尔斯·惠斯通和美国发明家摩尔斯几乎同时各自独立发明了电报。到了1866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前夕,美国实业家菲尔德(Cyrus West Field)成功铺设了跨越大西洋的电报电缆,将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连成了一体。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通信和信息技术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它们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除了电灯之外,最让人兴奋的发明当属电话和无线电了。再往后,电视、雷达、远程无线通信相继出现。而到了信息时代,大部分重大的发明都和通信有关,包括计算机、半导体、卫星、互联网、移动通信、智能手机,等等。今天(2008—2017年),全世界通信产业的产值达到了4万亿美元,接近整个日本的GDP。这还不包括计算机和半导体产业的收人。
二战之后,信息革命的另一大成果是破解了人类自身,乃至生命本身的信息。上个世纪50年代初,英美两国的科学家沃森、克里克、富兰克林和威尔金森等人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从根本上破解了生命形成的信息。以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生物技术,在信息革命的全过程中扮演了和IT技术几乎同等重要的角色。在未来的智能革命中,利用IT技术以及基因中的信息,改变人类生活特别是帮助人类救治疾病,延缓衰老,已是IT行业和生物医疗行业的共识。
把握了能量和信息这两把钥匙,我们就能洞察未来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变迁。
既然是技术革命,很多现有的技术必然会被淘汰,现有的产业和工作机会会消失,在很多人的印象中,IT行业是吃青春饭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样,由于技术变化快,以至于一些企业不愿意投资开发新技术,宁可山寨别人的东西。然而,在历次工业革命中,总会有一些变化慢的要素,伴随着其他不断快速变化的事物。一个聪明的企业家,会一直把握住不变的要素,长期投资那些影响力长远的技术,同时通过收购获得必需但是经常变化的技术。
那么什么是不变的要素呢?首先是上面所说的信息和能量。把握住这两样不变的要素,就能利用新技术在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举例来说,淘宝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卖场的信息化。今天在中国颇为流行的共享单车,其实本身的技术含量并不高,车还是原来的自行车,经营的方式与过去的租赁也没有太多的区别,但是将每一辆自行车信息化,能够通过手机和周围的自行车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就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近年来,人工智能是全世界关注的热门领域。而在人工智能中,以Google的TPU和英伟达的Xavier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芯片又是其中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TPU和Xavier的本质,其实就是在同样的单位能耗下,提供更高的计算能力。今天,集成电路内部的能量密度已经远远高于核反应堆内的能量密度了,而目大部分能量消耗在发热而不是计算上。因此,在接下来的智能革命中,芯片的能耗便成为提供机器智能的一个瓶颈。因此,这也就成为了Google和英伟达公司创新的方向。
除了信息与能量,下面这几件事情是一直都没有改变的:
对服务的需求;
对高端人才的需求;
对品质的需求;
对新事物的好奇。
对于高端人才的需求自不用说,这一点我们在本章稍后还会讲到。对于品质的需求其实也是永恒的。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希望上好的学校,在好的医院看病,只要支付得起,都愿意倬用高品质的商品。
说到服务,就不得不再次提到前面介绍过的“蓝色巨人”IBM。IBM的核心商业模式是什么?很多人会想到办公设备(在它进人计算机领域之前)、计算机系统、软件和IT服务。其实IBM的基因是服务,只是在不同的年代社会上所需要的服务发生了变化,它便随之不断地转型,更换服务的内容。当IBM引领世界计算机产业时,它很大一部分收人就来自于服务。后来随着个人电脑逐步取代大型机,IT服务在IBM的收人占比迅速提升。在2002年,IBM收购普华永道(PWC)全部的咨询业务,成为全球最大的咨询公司。今天,IBM来自计算机系统的收人只占总收入的10%,而咨询服务(两个部门)和IT服务各占了大约44%,其余为金融服务。很多人觉得今天的IBM在IT领域已经沦为二流公司了,但是只要全世界的服务产业还在,它就永远有生意做。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对新事物的好奇是不断增加的。拉斯维加斯每年的消费电子展(CES)会吸引近20万名注册参观者,而目这一人数每年还在增加。拉斯维加斯几乎没有国际航班,到亚洲和欧洲都需要转机。很多人不辞辛苦,从亚洲和欧洲跨越大洋万里迢迢专程赶来,就是好奇每年都会有什么样的新IT产品出现。
在不断变化的事物中,有些事物变化比较快,有些则变化相对缓慢,弄清楚其中的规律,对把握未来非常重要。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在计算机学术界发生了两件影响力比较大的事情,即方便计算机在商业中应用的COBOL程序语言标准的确立,以及高德纳等人以计算复杂度为核心的算法原理的确立。今天,不仅没有人继续使用COBOL语言了,而且即倬在图书馆里也很难找到当年占满书架的相关图书了。从COBOL开始,最流行的商用编程语言已经经历了四五代的变迁。然而,高德纳大部头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丛书不仅依然卖得很好,包括盖茨在内的商业巨子们依然对他推崇备至。事实上,只要读通了这套书,微软、Google等公司的工作便随你挑选。当然,这套丛书体量太大,它的一个更新的精简版《算法导论》(成书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则是求职上述公司的面试宝典。从这里可以看出,技术的呈现方式会变化得很快,而基础技术本身适用时间则是相当长的。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不妨再看一个更具体的例子—一计算机的存储。
计算机最初的存储靠的是卡片和纸带。它们的生命周期比想象得要长,一直倬用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第二代则是磁存储,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一直倬用至今。接下来是激光存储,大家过去在家看电影用的DVD就属于这一类。当下比较热门、用得比较多的则是固态物理(也就是半导体)存储,包括各种闪存卡和SSD硬盘。今天,人们已经开始研究利用生物材料比如DNA做存储的载体,并目在实验室里获得了成功。当然,每一代存储还可以往下细分,比如磁存储可以分为磁鼓、磁带、软磁盘、硬磁盘,等等。用不了多少年,存储的媒介都会发生更新和革命,一批曾经驰骋风云的公司就会消失,因为从纸质存储到磁存储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从磁存储再到激光存储,情况也相似。但是,与存储相关的很多基本技术,比如虚拟存储(虚拟化)、分层次的存储(Storage Hierarchy),存储的编码(包括压缩编码、加密编码等),存储的管理,包括目录、检索和随机访问等,不仅变化不大,而且继承性特别好。也就是说,这些领域的新技术几乎无法脱离原有技术而存在。
再往前看,汽车的内燃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有了不知多少代的改进,如今一辆汽缸容量不是很大的跑车,输出的功率是当初本茨和戴姆勒所发明汽车的几百倍,它们所用的技术和材料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相差百年的汽车内燃机,其工作原理依然是奥托循环,而燃烧的原理也大致相同。这就是快速变化和缓慢变化的区别。
理解了历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线索,我们无论是作为企业还是个人,都应该很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前进的方向和应该避免的陷阱了。
2 颠覆式创新
……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颠覆式创新的特点了。
首先要有一个杀手功能。蒸汽船的杀手锏是逆风逆流航行,微软是个人能够支付的电脑价格,Google是互联网的连接效应,ARM是低功耗,苹果是触屏、照相机等常用的非语音功能。没有杀手锏,什么都免谈。
其次,颠覆者的杀手功能必须容易得到当时相关技术的帮助,以至于进步飞快,而传统的产品难以受益于当时的技术进步,这一点是很多人所忽视的!蒸汽船受益于机械革命,微软受益于摩尔定律,Google受益于互联网,ARM受益于移动互联网,苹果则受益于信息时代的多种技术。在历届工业革命的过程中,永远不乏好的技术,但是孤立的技术进步并不能实现颠覆式的创新,任何成功的颠覆,都受益于那个时代其他技术的帮助。
再其次,正如同初生的婴儿都是不美的一样,颠覆式创新一开始一定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蒸汽船不可靠,微软和Google功能弱,ARM的处理器速度慢,苹果的手机价格昂贵。但是因为它具有一个或者多个杀手锏,当周边技术能够帮助它克服缺陷,并且不断放大杀手锏的威力时,颠覆过去占统治地位的产品和商业,就成为了必然。
颠覆式创新构成了历代工业革命的主旋律,它不是媒体上空洞的辞藻,不是随意、破坏性的试错,而是利用整个时代的技术进步一步步完成技术革命的过程。上述这三条规律概括了各个颠覆式创新的共性,可谓是它的范式。另一方面,在历次工业革命中,真正实现颠覆式创新的案例并不多,这才让它们显得格外耀眼,引人瞩目。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时代的颠覆式创新最终能够完成,但是具体由谁来完成,其实运气成分很大。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讲,也不必因为好运没有降临到自己头上而懊恼,因为在每一次工业革命中都会有很多的机会。要想把握住这些机会,就需要了解工业革命的本质特征和范式。
3 工业革命的范式
……
在这一节的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三次工业革命具有的共同特点。
首先,历次工业革命,必然会有一个核心的技术。第一次是蒸汽机,第二次是电,第三次是计算机和半导体。既然是能够改变世界的核心技术,它就一定不会是在一瞬间诞生的,因此每一次工业革命的科学基础都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而且要在很多年以后才会变成生产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中还会详述。
接下来,有核心技术就会有核心受益的人群。从18一19世纪的瓦特和博尔顿,到19世纪末的爱迪生和西门子,再到我们这个时代的IT精英们,都是其中的代表。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每次重大技术革命所带来的辐射效应,它会不断改造旧产业,缔造新产业,我们把这样的规律总结成:
现有产业+新技术=新的产业
而处于核心的新技术,其实并不需要所有人都去做它。
当然,由于技术革命影响的范围巨大,因此,在其他领域善用新技术的人也就自然成了它们的巨大受益者。
4 第四次工业革命
结束语
我们这一章主要都在回顾过去,但回顾过去,目的是为了展望未来。在以往三次技术革命中显现出来的规律,今天在智能革命中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概括来说,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有其核心技术和核心受益人群,都有早在几十年前就准备好的科学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能够称得上是一次工业革命的变革,辐射力是相当强的,很多产业都会随之变化,这就是机会所在。因此,历次工业革命都会有一大批核心产业之外的受益群体,都会按照下面这个范式诞生出新的产业,即
现有产业+新技术=新的产业
过去如此,未来也是如此。
第29章 信息时代的科学基础
1 从机械论到“三论”
……
在工业时代,企业的管理哲学是与其生产过程的这种确定性相适应的,其核心是追求效率。对此,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美国经典管理学大师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1856一1915)总结出了一整套适合工业社会的管理经验,并将它们写成《科学管理原理》一书。虽然今天和泰勒的时代已经相隔100多年,但是在很多企业中依然可以看到他的学说的痕迹。泰勒的管理学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 效率优先
提高效率,是泰勒管理学理论的核心。在泰勒看来,劳动生产率是区分文明国家和未进人文明社会国家的标准,因为生产效率的提升会将奢侈品变成必需品,让全社会都能享受文明的成果。工业革命之后,世界上一个个国家脱贫致富,靠的都是提高生产效率。比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老百姓们对拥有自己的汽车连想都不敢想,但是在短短的20年后私家车不仅在社会上普及了,而目开始“泛滥”了。这一切改变,都拜生产效率提高之赐。
那么怎样才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呢?泰勒最看重的是优化流程和标准化管理。
泰勒是从底层工人做起的,最能体会到每个工人的操作中有多少流程是可以优化的。在他的管理生涯中,他对生产的每一个步骤都不断地做试验,以找出每个工序的最优操作方式,并目教给工人们。这样一来,整个工厂的生产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了。泰勒提高生产效率的第二个法宝,是将一切都标准化,既包括部件的标准化,也包括管理流程的标准化,后者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ISO标准的理论基础。优化流程和将一切标准化,倬得大规模流水生产线成为可能。当然,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那样,泰勒的这种过程优化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复杂的产品一定可以分解为简单的部分,而目一切结果都是可预知的,这就如同哈雷将彗星的参数代人行星运动的方程,一定能预知它们返回的时间一样。但是,对于艺术品的创作,泰勒的方法不管用,因为艺术品很难拆解。我们后面还会看到,对于今天的很多IT产品和服务,泰勒的办法也不管用,因为它们的结果不可预期。
当企业按照泰勒指引的方向优化流程时,整个工厂就变成了一个大机器,而工人则变成了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喜剧表演大师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就生动地反映了在这个时代里“社会人”变成“机器人”的事实。在那样的工厂里,除了工厂主和主要的工程师之外,没有人知道产品生产过程的全貌,因为他们不需要知道,一切都是按照事先设定的流程进行的。因此,生产线上的工人和工业革命早期的工匠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的工人缺乏工匠精神,这并非工人们不努力,而是为了追求效率设计出的生产方式让他们无法成为工匠。事实上,不仅当代中国缺乏工匠,在深受泰勒管理思想影响的美国也缺乏工匠,因为大部分工人只需完成生产线上一个环节的简单工作。今天,或许只有在不以追求效率为目标的日本、德国和瑞士的一些小作坊,包括法国的奢侈品加工厂,才能找到做产品精益求精的工匠。此外,当标准化取代了个性化之后,效率得到了提升,生产出来的东西则是千篇一律。
如今,不仅工业企业中依然有泰勒管理的影子,在一些IT企业中也是如此。比如在软件工程中,传统方法是由个别架构师先做设计,然后一级级向下做详细设计,最后由程序员编写程序,还有专门的测试人员进行测试。除了那些做上层整体设计的(相当于过去生产线上的工程师)人对产品整体有一定的了解外,其他人只负责写功能定义得非常清晰的程序模块。因此,IT行业把写这种程序模块的工程师称为“码农”,易不大好听,却也是很形象的比喻。完善泰勒现代管理理论的另一位大师是甘特(Henry Laurence Gantt,1861一1919),他发明的甘特图原本用于管理工厂生产进度,经过调整和优化后,甘特图现在经常被用在软件工程中管理软件项目开发进度。
- 同构的树状组织架构
泰勒管理方式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企业组织结构的设计,完全是为了适应这种自上而下将产品分解为大小任务的做法。具体来讲,就是企业组织采用十分严格的树状结构,且大小组织同构。比如一个汽车厂,它会按照产品分为几个分厂,比如整车厂、发动机厂、轮胎厂、传动设备厂,等等,每一个分厂里有若干生产线,每一条生产线都有工段,每一个工段都有小组。同一级不同的组织之间绝无交叉。图29.1是这种组织架构和相应的产品功能对应图。
图29.1 无交叉的组织架构与产品功能模块完全吻合
根据产品功能对行政组织进行严格划分的做法,在提高效率上有两个好处:其一是责权分明,也容易进行绩效考核。其二是容易培养出熟悉自身业务的管理人员。我们经常会看到工厂里有这样的晋升过程:小组长升工段长,工段长升分厂长,等到他们真的管理一个大工厂时,管理的方式其实和过去没有太多变化。
在一个产品形态稳定、行业变化慢的产业里,这样的组织架构能够让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效率较高,然而弊端也很明显,特别是在市场变化快、产品预期不明确的形势下。比如在今天的后信息时代,这种较为固定、边界清晰的管理模式,完全无法适应生命周期很短、失败率高的IT行业。
- 可预测性
机械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发现了普遍规律后,只要将其应用到具体场景,便一定能够预知结果。比如,蒸汽机车烧掉若干吨煤,一定能够跑出100千米;工厂每一万元的产值耗电量是多少;普通民众每月的日用品消费是多少,等等。这和运用牛顿力学原理预测一千年后的日月星辰运动没有本质差别。正是充分利用了这种可预知性,丰田公司甚至可以做到组装厂没有库存,因为当生产线上的零部件快用完时,下一批零部件会及时运到。这样便大大降低了库存成本,也大大减少了汽车进出库的时间。当然,在工业时代过度的预测会有害无益。苏联在工业规划上不仅认定工厂内的所有生产计划都是可预知的,甚至试图预测市场。苏联政府拥有规模庞大的各级计划部门来做预测,但是效果明显不佳。
到了信息时代,预测的准确性和可能性大大降低,倬得预测变得不再有意义。2010年腾讯公司最挣钱的产品是一款鼓励玩家偷菜的农场游戏,每天有几百万元的收入,但是过了不到一年,这款游戏的收人就陡降至每天几百元,公司内外没有人能预测出这个结果。即便是同一种产品,各种功能的倬用频率,常常也不是设计者所能预测的。以手机为例,在过去的电信公司看来,手机主要就是用来通话的,因此它们试图通过提高话费来挣取更多的钱,这就如同石油公司通过控制油价最大化利润一样。但是,它们想不到的是,用户更多地倬用了短信以及短信的替代服务,这在无意中便造就了腾讯这样的公司。
- 人性化管理
易然很多人都诟病泰勒将社会的人变成了机器的人,可这其实并不是他的本意。底层出身的泰勒深知工人们怠工的普遍原因,他知道只有劳资双方同时进行精神革命——资方善待工人,工人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才能进一步提高效率;作为对工人努力的回报,雇主则必须对工人给予物质刺激,包括发放奖金和福利。因此,这种管理模式也被称为“积极性 + 刺激性”式的管理,俗称“胡萝卜+大棒”。
管理学界在说到泰勒的科学化管理时,会举出很多亨利·福特的例子,因为他是泰勒式管理的实践者。据说福特曾做过一个梦,梦见每一个自食其力的美国人都有一辆福特车,与家人一起在广袤土地上共享快乐时光。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支付给工人很高的工资,以便让他们买得起汽车。二战结束后,日本人把泰勒的这种人性化管理方式发挥到了极致。在很多日本企业里,员工一旦进入一家公司,基本上就是一直干到退休,公司会包管员工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作为对公司的回报,员工要努力工作,对公司保持忠诚。
泰勒的这种管理理念在20世纪初缓和劳资矛盾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泰勒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利润分配本身是一个零和游戏,资方拿的多了,劳方就拿的少,反之亦然。这就如同经典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原理一样。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这个矛盾并不突出。美国应用泰勒管理最成功的年代是20世纪初,那个时代被称为“柯立芝繁荣”。日本采用这种管理方式最成功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那是工业时代最后的辉煌。但是,当经济陷入萧条时,劳资双方的零和游戏就变得火药味十足,就连一向善待劳工的福特都开始非常残酷地压榨工人。随着后来劳资双方的力量往劳工一方倾斜之后,企业因为利润难以得到保障,便陷人了“破产保护——违约一—清除不良资产和员工福利一一重新盈利—一过度福利一一破产保护”的怪圈,在其中反复循环。这些企业今天被称为“僵尸企业”,在美国、日本和欧洲存在着大量类似的僵尸企业,其根源在于分配制度出了问题。
当历史进人到1946年时,时代变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了,它标志着信息时代即将到来。既然时代不同了,就需要有不同的科学基础和方法论,以便支撑起新的管理方式和文化。凑巧的是,几乎就在电子计算机出现的同时,信息时代的方法论也产生了。
1948年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寻常的年份,但就是在这一年,对现代科技和工业发展影响深远的一些学说—一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正式诞生了,它们造就了信息时代的方法论。这些学术成果其实早在二战期间就已产生并目得到了应用,只是因为战争的原因,美国才没有发布。到1948年,二战结束三年后,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众了。
控制论的创始人是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894一1964),他被誉为20世纪最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天才。维纳在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之前曾经在清华大学做过一年的教授。他这段时间的工作十分轻松,有大把闲暇时间用来思考数学问题,并目开始在头脑里酝酿着一套全新的理论。后来,他把这段时光称为自己学术生涯里一个特定的里程碑,因为那是他从一位学富五车的科学天才,变成一位开创全新领域的大师的转折点,而他酝酿出的理论就是控制论。1948年他出版了《控制论》一书。
也是在1948年,美国的另一位科学天才克劳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1916—2001)在《贝尔系统技术杂志》(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上连载发表了论文《通信的数学原理》(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从此通信进人了具有理论指导的时代。1937年,香农完成了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硕士学位论文一—《继电器和开关电路的信号分析》(A Symbolic Analysis of Relay and Switching Circuits),奠定了今日数字电路的基础。二战期间,有大量的通信和信息处理工作,香农参与了为军方服务的工作,他的信息论其实是在那段时间里完成的,只是到了战后才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维纳和香农当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理论后来不仅让人类完成了登月壮举,让全世界通过互联网的连接变成了地球村,而目缔造出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经济发展模式,从此,人类步人一个新的时代一—信息时代。
与控制论和信息论同期诞生的还有贝塔朗菲(Karl von Bertalanffy,1901—1972)等人提出的系统论,系统论对后工业时代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战期间,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在负责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主动采用了系统论进行项目管理,大大缩短了原子弹的研究进程。这让当时连玻尔等科学家都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得以在短短的三年内完成。
今天,人们将系统论和控制论、信息论并称为“三论”。硅谷的各种管理特点,用牛顿力学和泰勒的现代科学管理思想是完全解释不通的,甚至是相违背的,但是若用三论的观点去分析就一目了然了。因此,破解硅谷地区和它的企业成功的奥秘,就需要用到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这些钥匙。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们和信息时代管理特点之间的联系。
2 方法论的革命
3 信息时代思维指南
硅谷企业的很多行为实际上都是对现代工业企业制度的否定。比如那些大公司很少建立传统的研发实验室,企业很少对未来做预测。又比如硅谷的企业很少教育员工对企业的忠诚,甚至整个硅谷地区从公权力到基层社会会鼓励叛逆行为。如果单纯看硅谷公司做事情的方法,只能得到浅层面的理解,甚至会产生误读。如果简单地从表面理解学习它们的经验,不仅不利于事业发展,而目可能会落入陷阱。只有深刻理解以硅谷企业为代表的信息时代企业行事的理论基础和逻辑,才能得到硅谷方法论的精髓。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对比新旧时代的不同做事方法,剖析信息时代方法论的科学依据。
3.1 预测vs. 反应
……
当然,在信息时代能够淡化预测、实现快速反应,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知识型工作者自身的自觉性。在大工业时代,这一点则做不到。现代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他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一书中指出,每一个知识工作者本身就是一个自觉的自我管理者,对于他们不能也不需要采用过去那种简单的自上而下的人事管理方式,而要改成任务导向的契约式管理方式。他的这种思想被信息时代的很多管理者,包括比尔·盖茨、格鲁夫和Google前CEO施密特所推崇。在硅谷的IT公司,每一个工程师不仅在作息时间上相当自由,也是公司基层决策的参与者。他们的自觉性倬得公司能够根据最新的变化做出快速反应。
3.2 拥有vs. 连接
……
在所有连接中,处于关键路径上绕不过去的那个节点最有价值。在个人电脑时代,整个PC产业链中绕不过去的两个环节是微软的操作系统和英特尔的处理器,这两家公司也就先后成为那个时代市值最高的公司(市值都曾超过5000亿美元)。在今天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关键节点并不掌握在一家手里,而是在几家IT巨头手里。微软依然牢牢把握着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但是Google掌握着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安卓操作系统,而亚马逊的云计算平台起到了企业级云计算操作系统的作用。再加上自成一体的苹果,它们成为了今天全世界市值最大,而目在各自领域无人能够挑战的公司。
3.3 局部vs. 整体
大工业时代的宿命,是一个地区的产业转型很难,以至于无法在下一次科技进步中继续引领潮流。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是地区对大公司的依赖。
在大工业时代,一个地区的发展常常仰赖一个核心产业,甚至是这个产业里的一两家大公司,很多小公司都围绕着一两家大公司运转,当这一两家公司过了气,整个地区也就衰落了。这似乎是大工业时代的宿命。以美国为例,匹兹堡的发展靠的是钢铁业,具体来说靠的是卡内基钢铁公司这一家公司;底特律靠的是三大汽车公司;新泽西靠的是基于电话的电信产业,而目基本上靠的是AT&T这一家公司(当然今天它派生出了很多公司);而在纽约的北部(即上纽约地区),从19世纪末开始,当地经济基本上就靠IBM和GE这两家公司支撑。这些公司一方面像一把大伞保护着当地,并目为当地带来了迅速的繁荣,比如像地处美国内地的匹兹堡和底特律,当年之所以能够崛起,不能不感谢卡内基钢铁公司和三大汽车公司。再比如像通过微软一家公司带来繁荣的西雅图周边地区,但是这些公司规模都太大了,在它们的阴影下,不可能再成长出大树了。一旦大树倒掉,当地的经济便将受到重创。正因如此,当地各种利益集团都不敢让大树倒掉,只要能多支撑一天就要让它们继续维持着。但是,如果跳出这些地区,或者过了很多年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优化了局部利益,而牺牲了一个地区整体发展和长远的利益。
其次,一个产业里最好的公司难以走出这个产业。
如果说大公司决定了一个地区的行业导向,使得政策向现有产业倾斜,导致一个地区无法实现转型,那么为什么这些大公司的内部转型也非常困难呢?大部分时候,不是这些公司不想转型—一他们的高级管理层通常都很优秀,而是根本转不了,因为公司的基因和文化是公司成立之初确立的,受到当时产业环境的制约。当一个公司从小到大成长起来时,只有适应那个产业特点的(创始)人和公司才最终生存了下来,可以说那些公司的基因和企业文化的形成必然有其合理性。比如IBM早期向客户收取高额服务费的做法,我们今天看起来实在是太“心黑”,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只有专家才会使用计算机,IBM派人进驻客户,帮助客户使用计算机,是有利于计算机普及的。但是,当大公司的组织架构和管理风格不断优化到最适合现有业务时,它其实就很难再适应新的业务,这就是惯性原理在起作用。以微软为例,它的组织架构和Office软件的层次结构几乎完全吻合,以这种组织架构来开发互联网产品,自然会力不从心。
一个传统工业区、一个大公司,越是对现有企业、对现有业务进行局部优化,就越难以在较长时间和空间内做全局优化。从控制论的角度看,在当前利益基础上优化得越多,就越容易陷人“局部最大值”,也就是走入了一个进化的死胡同。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很多地区在高速发展了一段时间后,便走到了尽头。
……
4 企业制度背后的科学原理
硅谷的成功是基于对现代工业企业的否定,当然它也形成了适合信息时代企业发展的新的企业制度,而那些新的企业制度的背后,有其科学原理。
4.1 宽容失败的背后
在工业时代,一个大企业为了更好地预测未来的技术发展趋势,通常会创办自己的研究部门,像AT&T的贝尔实验室、GE的RCA实验室和IBM的沃森实验室,等等。这些部门负责看清楚未来,而公司的业务部门则沿着规划好的方向继续发展。成立独立研究部门的好处有很多,比如研究部门的人不用太考虑商业上的成本,研究工作可以比较超前,一旦研究失败,不会影响到当前的业务。不过这样一来,即使有了研究成果,转换成改变世界的产品,也是千难万难,绝大部分研究成果最后就束之高阁了。今天,IBM每年获得世界上最多的专利,但是你并没有觉得它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发明,因为那些发明没有产生效果。
到了信息时代,上述节奏已经赶不上技术的变化了。我们在前面提到,Google的研发效率来源于研究者和开发者合二为一,它不经过对新技术的验证期,直接就在市场上开始尝试了。而Facebook在这方面更激进,它甚至将不成熟的,甚至明显荒诞的想法推向市场,然后通过市场的反应进行必要的筛选和剪枝。当然这样做失败率很高,而且一旦失败,损失很大。Google尝试了报纸广告业务、很多版的社交软件、电视机顶盒、各种电器的智能面板、Google眼镜等许多产品,都失败了,每次失败都损失巨大,但是它能够宽容失败,这才在安卓操作系统、Chrome浏览器、人工智能和无人驾驶汽车上取得了成功。可以说,能否宽容失败,已成为新时代公司成败的关键。
硅谷能够宽容失败,这首先得益于美国这个国家比较宽容失败,当然硅谷在这方面又更进了一步。这里面有一个历史的因素,即1948年之前硅谷并没有像样的工业,很少受工业时代定势思维的影响。类似地,全世界在美国之后第二个宽容失败的国家是以色列,它在1948年才建国,不仅没有工业,甚至没有传统的包袱。无论是硅谷还是以色列,第一个重要的产业就是信息产业,于是便很自然地采用了三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企业管理。如此一来,硅谷地区对失败的认识和对失败者的态度就跟其他地区完全不同了。
硅谷公司首先在宏观上认可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并目会把失败计入成本预算。硅谷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预言家告诉大家该怎么做事,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都是依靠反应而不是预测去行动。前面说到,硅谷的企业和风险投资会把最好的资源分配给最有可能成功的事情,但是在看似不太可能做成的事情上,它也预留了一些资源,毕竟没有人事先知道结果。当然,在控制风险时,它们在一开始就把失败的成本考虑进去了,因此当失败真的发生时,也不会有人给失败者贴上标签。
宽容失败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成本的上升。很多人抱怨苹果的手机卖得太贵,或者思科的路由器利润率定得太高。其实原因很简单,作为行业里最早吃螃蟹的人,它们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失败才获得成功,由此要将失败的成本都摊到每一个成功的产品里去。通常,硅谷的半导体公司都会追求30%以上的毛利率,而其他公司(比如系统设备和软件公司)则把毛利率的目标定在50%左右。这样也就逼着硅谷的公司要做出技术领先、利润率高的产品。据美满公司前CTO吴子宁博士介绍,在硅谷的半导体行业,毛利率低于20%的事情是肯定不会去做的,而台湾的半导体公司甚至会考虑去做毛利率只有5%的事情,因为后者没有失败的成本,当然也就无法引领科技发展。
中国在经历了“双创”提法已深人人心的阶段之后,大家对投资的失败、创业的失败变得宽容了很多。但是,在绝大部分公司的内部,对失败依然不宽容。而越是不宽容失败的企业,也就越没有活力,而目还在不断失去过去的市场。在这样的企业中,一些国企最有代表性。在国企中,谁要是因为大胆做事损失掉一个亿,那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犯错者不仅要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而目还可能被人背后猜疑是否有道德问题。其实,如今的一亿元人民币,对于商业来说,金额并不算大,从购买力来说,也就是北京或上海的一两套顶级住房,和中国十万亿的GDP和上百万亿元人民币的发行量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在Google,程序中一个很小的Bug有时会造成几百万美元的损失,历史上最多的时候造成过几千万美元的损失,但是Google从来没有因此处罚过任何工程师。相比之下,中国的一些企业,特别是国企,里面的主管似乎都患上了失败恐惧症。世界上任何一种创新都有可能伴随着失败。宽容失败,从本质上讲,是对不确定性的认可。
4.2 期权背后的科学
硅谷企业的分配制度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给员工发放期权(Option)。注意,期权不是股票,它是一种特殊的金融合约,是合约的一方给另一方在一定期限里按照某个价钱购买(Call)或出售(Put)股票的权利。比如,阿里巴巴公司的股票(代号BABA)在2015年8月12日的收盘价格是每股75.12美元,阿里巴巴或者某家证券公司(Underwriter)给予期权的所有者在10年内任何时候,以这个价格(称为Strike Price)买进这家公司股票的权利,公司给员工的就是这种买人期权。如果在十年内的任何时候股价比当初上涨了,期权的所有者就获得了差距的利润。比如2019年1月11日,阿里巴巴股票的收盘价是151.32美元,期权的拥有者依然能够以75.12美元的价格买人股票,从而赚取大约一倍的溢价。如果10年内股价从来没有超过75.12美元,期权的持有者不用做任何事情,既不赔钱也不赚钱。图29.6显示了股价和期权利润之间的关系,当股价达不到期权授予的价格时,期权的利润为零,当然握有期权的员工也不会损失什么。当股价超过期权授予的价格时,期权的收益和股价呈线性增长关系。
图29.6 股价和期权利润的关系
当然,期权并不能随意发行。因为被授予期权的员工一旦行倬(Exercise)期权后,这家公司的流通股就增加了,股价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样既损害了投资人的利益,也让期权变得一文不值。因此,一家企业能发放多少期权,其实要看业绩增长,期权增发的比例,不应超过利润增长的幅度,否则股价就会下跌。此外,2000年之后,美国证监会对期权发放有非常严格的限制,而目要求将期权像奖金一样计人成本。
期权制度的本质是从存量分配变为增量分配。期权要想不变成废纸,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利润的提升,让市场肯定公司的表现,进而推动股价上涨。拥有期权的员工有足够的动力和老板一起,把公司办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和公司之间分配的是未来业绩的增量,而不是财富存量。劳资之间、上下级之间的那种相互对立的矛盾关系就变成了相互合作的契约关系。至于增量如何分配,就得看当初每个人和公司签的合同是什么样的。公司作为在某个行业里已经打下一定基础的实体,为员工提供了一个发展平台,这个平台相当于公司的投资资本,而员工以前的经验和他所拥有的资源(市场资源、技术专利等),相当于员工投资的资本。双方通过谈判,签订一份财富增量分配契约(劳动合同),从此就开始了合作,而不是先前那种雇佣的关系。我在各大商学院讲课时,很多企业家学员抱怨如今招人太难,留人更难。我认为在如今的后信息时代,一个企业“请”一个人来做事情,要本着企业与个人合作的心态,做不到这一点,要想留住人确实不容易。一些企业家,明明做的已经是新时代的生意,想法却还停留在旧时代,他们在给员工发放期权时,总认为这是企业对个人的恩赐。其实,期权只是一种财富增量分配的合约,本身不具有价值,它的价值是员工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的,并非企业从已有蛋糕中分给员工的。依靠期权制度来进行的财富分配,财富来自投资人,而非公司本身的利润,本质上是市场(投资人)对公司表现的一种反应,这和风险投资“加倍投入”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投资人在一开始对各种技术和相应公司的前景所知甚少,因此他们并不需要做预测,时间一长,公司的好坏就看得很清楚了。对表现好的公司予以肯定,投资人会更多地买人这些公司的股票,这些公司的股价就会上涨,公司所有者和员工都会有巨大的经济收益,公司因此而稳定,有可能做得更好。而经营不善的公司,市场对它们的股票反应冷淡,员工的期权就成了废纸,公司可能最终解体或被并购。于是,通过期权制度,资本和资源就流向了表现好的公司。
期权是信息时代的分配制度,从公司内部看,是对增量的分成;从公司外部看,是投资人通过资本对新技术和新技术公司的投票。这种分配方式不仅将企业主、资本和劳动者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形成了合力,而目资源的使用效率也得以最大化。
4.3 扁平式管理的本质
在一个公司里,要想合作顺畅,首先需要做到信息交流和沟通顺畅。比如上级的指令需要以最低成本下达,下面的反馈需要以最快速度上传,同事之间坦诚而高效地沟通,分属于不同部门的合作者需要最快捷地交换信息,这些都是保证合作持续稳步进行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通信,是信息的传递。根据香农第二定律,信息传递的速率受制于带宽,一个公司有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就决定了这个组织结构中沟通的带宽。
图29.7 硅谷某公司的全员大会,形式相当随意
在传统的层级分明的树状管理结构中,信息是一层层下达的,如果汇报关系有六级,很多信息便要经过五次才能传递给基层员工,而目在传递的过程中,一些中层主管们还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者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出发,曲解或者保留了公司最高层的本意。在硅谷的公司里,需要定期和不定期地召开全公司或整个部门的全员大会(图29.7),这样就能以最低成本,快速目不失真地传递公司的精神。在硅谷以外的公司里,这种全员大会并不多,大部分时候都是公司的信息事先通知到管理层,再由管理层传达下去。
树状层级管理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同层级之间的员工在地位上有较大差异,上级对下级有很强的支配权甚至是生杀予夺的权力,上下级之间很难做到无保留的坦诚沟通。下级习惯报喜不报忧,中层习惯欺上瞒下,最高层习惯保持神秘感。经常会看到公司里有这样的现象,下级怕挨上级“骂”,便隐瞒一些问题,结果原本不大的问题最后变成大麻烦。在通信上,这种有意无意藏匿或者歪曲一些事实的行为,相当于在要传输的信号中加人了人为的噪音,它们不仅倬得信息失真,而目为了消除噪声,就需要反复沟通确认,导致信息的传输速率大打折扣。
层级分明的树状管理结构的另一大问题,是部门之间沟通环节太多。每个部门都有着明确的边界,而目很多主管都把部门看作自己的私产,因此在两大部门内传递一个信息,有时需要层层上报,最后到两个部门的高层坐在一起商量出结果后,再层层下达。我在给国内一家大公司说课时曾经说过一个IBM的笑话一一“把一个箱子从二楼搬到三楼需要多长时间?”答案是4个月。因为在管理规矩严格的IBM,要搬这个箱子不能自己动手,必须由合同搬家公司来操作,而这件事又不能由员工直接找到搬家公司下任务单,因为搬家公司不会接受。总之,这个员工先要层层上报,得到有关部门批准后,再把指令下达给公司的物流管理部门,再由该部门通知搬家公司,最后搬家公司排出任务单,根据任务的优先级安排一个时间完成搬运工作。讲完这个笑话,下面的听众都哈哈大笑,但是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现象在他们身边比比皆是,只不过不是针对搬箱子的流程,而是部门间合作的流程。在这家公司里,一个部门想要采用另一个部门的研究成果,而提出需求的人无法直接找到对方具体做事情的人,因此他需要向自己的上级提出需求,他的上级,甚至是上级的上级,再找到对方平级的主管来表达这个意愿后,如果对方不反对,才会通知下面具体做事情的人将成果分享出去。一来二去的,时间就耽搁了。
真正的扁平式管理是什么样的呢?除了层级总数减少以外,树状结构还变成了格状甚至网状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公司的不同组织之间存在着很多虚拟的通道,倬得信息能够直接传递,不必经过很多节点和关键路径。上下级之间能够坦诚交流,大大减少了通信过程中的噪声,信息传递快。当然,这种相互信任的前提,是公司里不同层级的人之间没有太大地位上的差别。
有效的通信是需要有一个协议的,发送端和接收端在通信时都必须遵守协议,这样才能保证通信的正确性和系统之间的兼容性,否则就会出现错误。在公司内部进行沟通也需要协议,这个协议就是一种契约精神,公司和员工之间是靠这种契约维系的,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都是如此。
工业时代和后信息时代的公司,其内部沟通渠道之间的差异,有点像20世纪初的长途电话网络和今天的互联网之间的差别。前一种通信系统由很多信道串行而成,当跨越北美大陆的第一个长途电话从纽约打到旧金山时,中间经过了10多次转接才完成,在这个系列串行的路径上,每一段都是关键路径,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通信就中断了。而在后信息时代,扁平化管理的公司,其内部沟通渠道相当于互联网,一个信息从北京传到深圳,中间没有阻隔,而且有多个渠道并行传递,不存在很多的关键节点和关键路径,沟通起来要顺畅得多。从本质上讲,扁平式管理的科学基础就是增加带宽,使沟通变得顺畅,合作变得容易(见图 29.8)。
图29.8 传统管理结构通常是严格树状的,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渠道很长(实线)。硅谷IT公司在不同组织之间建立了网状联系(虚线),沟通要顺畅得多。
扁平式管理的另一个特点是分权,这一方面减少了不必要的通信,另一方面可以将最宝贵的资源(公司金字塔顶端管理者的时间)用于最重要的工作,将更容易获得的资源(中层主管的时间)用于相对次要一点的工作,这与霍夫曼编码原理相一致。
总之,扁平式管理拓展了公司内部的带宽,倬得公司内部的合作更顺畅,才能做出最好的产品和服务。在大工业时代,效率来自于事先的规划和不断重复的操作;而在信息时代,效率来自于沟通的带宽,以及共同遵守的协议。
4.4 权威失灵的背后原因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女王对一群经济学家讲,你们这么多经济学家,怎么没有一个人提前预见到金融危机,当时在场的经济学家都觉得很没面子。这倒不是经济学家们学识不够,而是因为今天要做预测实在太难了。从2000年开始,世界上一直有经济学家预言中国的经济要崩溃,这件事一直没有发生,即倬未来发生一次,那种预测的准确性甚至比不走的钟还糟糕,因为不走的钟一天也能准上两次。
不仅经济学家无法预测未来,IT产业的专家的预言也常常很不靠谱。2007年,诺基亚时任CEO认为苹果的iPhone不会有多少人要,因为那些功能与电话无关,但是iPhone很快就开始风靡世界,而他却为自己的预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2004年,经济学家们预计驾驶汽车是计算机在短期内无法取代人的领域,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确实很难想象这件事能在几十年内实现。然而,仅仅过了6年,2010年《纽约时报》就报道Google的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在大街小巷和高速公路跑了十几万英里,而目没有出一次交通事故。
曾几何时,人们从不怀疑权威的正确性。但是今天,大家发现权威的远见性似乎比我们好不了多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信息时代,信息量太大,不确定性太多,以至于做出准确的预测变得几乎不可能。就说2008一2009年的那次金融危机吧,活着的经济学家基本上没有人经历过,没有人能相信它会来的那么凶猛。有人说经济学家们应该能从经济数据上看出端倪。但是,在美国各种经济数据有上万种,一个经济学家一辈子能研究清楚上百种就不错了。今天已经不是牛顿时代,用几个简单的公式就能把未来描述清楚。
权威不灵了的第二个原因,是世界发展太快,旧知识很快就过时了,这是在过去工业时代所没有的现象。在瓦特之前的时代,效率非常低的纽卡门蒸汽机使用了半个多世纪都没有什么改进;在爱迪生发明了高效率的白炽灯后的一百多年里,发光效率和灯泡寿命一直没有明显的改进;录音磁带从发明到基本退出舞台,经历了80年左右的时间,原理基本上没有变化。因此,在那个时代,专家经验的积累很有用。甚至在信息时代早期,一个专家依然可以靠一项专业特长工作一辈子。比如,2000年前后的数据库技术,和80年代初甲骨文以及IBM研发的关系型数据库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而1993年微软推出的Windows NT,其内核和1969年的UNIX没有本质的差别。在1998年Google成立之前,文献搜索技术基本上还是基于70年代初斯巴克–琼斯(Karen Spärck Jones)的TF IDF技术。但是,今天这种现象就很难持续了。靠人为积累起来的经验对今后工作的指导意义,远不如掌握更新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技术来得有效。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硅谷人不迷信权威。在信息时代,信息流通得非常快,与其让权威告诉你该怎么做,不如掌握最新技术后自己来分析信息。再加上今天的IT精英普遍基本训练水平很高,可以很快获得和掌握最新技术。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今天的硅谷人不喜欢崇拜权威。
当然,在美国不迷信权威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与美国的教育有关。在美国的学校里,学生们从小被告知问题的答案可以有很多种,不一定存在一个标准的答案,也不是对或者错的答案,而是把答案分为好的和不好的。年轻人不会因为某个结论是专家告知的就盲从,而是有自己的判断和主见。
总之,在今天这个时代,谁善于获取信息,有能力从信息中获得新知,谁就站在了时代的制高点。
4.5 从资源分配的有效性理解拒绝平庸
我们经常在媒体中看到有些专家学者发表这样的言论:某某地区生活成本太高,年轻人生活不下去,长此以往,该地区要衰退。在美国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当仙童公司将它的生产线转移到香港时,就有了唱衰硅谷的说法,最近一次比较有影响的唱衰硅谷的言论是2018年《经济学人》上的一篇文章,里面讲了很多原因,诸如生活成本上升,大公司福利过高,等等,结论就是硅谷将荣光不再。但是,唱衰了半个多世纪还在唱衰,说明它没有衰落。这不是运气倬然,而是背后有它长盛不衰的原动力,即拒绝平庸倒逼产生的进步。
图29.9是硅谷房价的变化和纳斯达克指数变化的对比。可以看出,在过去30多年里,硅谷房价(实线)不断攀升,从1996年到2017年增长了三倍左右,涨幅和持续的时间在美国都是绝无仅有。而在背后支持这一房价持续上涨的原因,主要是硅谷明星公司的财富以更快的速度积累所致。从图中可以看到,纳斯达克指数(虚线)在过去同一时期,增长了大约6倍多,远远高于硅谷房价的增长。在纳斯达克的成份股中,总部在硅谷的公司大约占了权重的一半,而其中的明星公司,包括苹果、Google、Facebook、英伟达和特斯拉等,其增长的幅度要远高于纳斯达克平均水平。我们前面说的硅谷公司股价上涨,员工将会受益,正是个人不断剧增的财富在支撑着硅谷的房价。一些媒体说硅谷房价的上涨超过了收入的增长,那是没有计人期权收益。在硅谷地区,同一类工作基本工资不会相差太大,但是每个人期权的收人很容易差出一两个数量级。期权收人高的买得起房子,这方面收人低甚至期权长期潜水的,几乎不可能在硅谷购房。
那么什么人能获得巨额的期权收益呢?主要是明星公司的骨干员工。期权收益的实质,是投资人对表现卓越的企业和个人的奖励,和长时间辛劳、平庸的表现无关。在很多地区、很多行业,一些平庸的企业可以通过压低自己的利润去占领市场,这样虽然挣得少一点,但总有口饭吃。这种做法在硅谷行不通,因为这种企业和它的员工都无法在硅谷生存。一个企业也好,一个人也好,要想在硅谷立足,就需要拒绝平庸,追求卓越,而且有时只是做到行业领先还不够,还要和任何其他行业的公司比都不落后才行。
图29.9 硅谷房价增长和纳斯达克指数增长的对比(数据来源:Paragon Read Estate Group)
以Google公司为例,2008年时,它在搜索、浏览器和云计算上跟微软有明显的竞争,和苹果相比也不落下风,比雅虎更是好到了天上。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它的整体成长速度和提供的好工作机会输给了当时快速发展的Facebook,易然后者和它在业务上重合度并不高。这样,Google的很多优秀员工就跑到Facebook去了,因为那样才可能买得起房子。Facebook的第一位华裔副总裁当时就是因为这一很实际的原因离开Google,到了对方公司。而他给周围很多工程师树立了榜样之后,他过去的同事也纷纷离开Google,去了Facebook。这类事情当时每个星期都在发生,这就倒逼了Google管理结构的调整和分权。此后,Google在同Facebook的竞争中便不再落下风了,很多离开Google到Facebook的员工又回流到Google了,这又倒逼了Facebook的改革。
2014年之后,Google又面临着Uber和Airbnb等未上市的独角兽公司的挑战,不少高管离职加人那些公司。其中Uber公司对Google的威胁尤其大,它发展迅猛,司机人数几乎呈指数上涨(图29.10),而目业务领域与Google一些长期布局的领域,比如无人驾驶汽车,有较大的重叠。外部压力导致Google做出了第二次重大调整,它将已有的业务(搜索、广告、安卓和YouTube)和新业务分离。稍微成规模的新业务,比如智能家居Nest、无人驾驶Waymo,大数据医疗Calico等,以及创新实验室X Lab,都变成了独立的公司,以保证新业务不受现有业务的影响,能够走出温室,在行业里更具竞争性。
图29.10 Uber司机在美国的增长速度,呈指数增长态势
在硅谷地区生存,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必须追求卓越,拒绝平庸,否则就会被淘汰。当我们看到苹果手机、Google无人驾驶汽车、英特尔和英伟达处理器在世界上占据了领先地位时,可曾想到这也是被硅谷环境倒逼出来的结果。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不断将资源从表现不好的公司手里拿走,再重新分配给那些更有发展潜力的新公司的过程。这在无形中是符合信息论的规律的。如果你把硅谷本身看成是一个最大的风险投资机构,它的这种结果和风险投资集中资源给最好的项目是类似的。只不过,风险投资的决策是由人决定的,而硅谷的资源分配是市场决定的。
5 大数据和互联网思维的本质
今天我们经常说大数据思维和互联网思维,这并非炒作概念,而是有它们背后的科学道理的。
5.1 大数据思维的科学基础
大数据的科学基础就是信息论,大量强相关数据的涌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这就是大数据思维。当然,这种改变最初是渐进的,到了互联网充分发展之后,量变就形成了质变。
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和“三论”的出现几乎是在同时。这并非巧合,因为它们都是人类遇到大量信息后,需要处理信息和利用信息的必然结果。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全世界的信息量突然暴增,从信息种类和信息量来说,都是过去不曾遇到过的,这些信息包括。
各种无线电信号信息,里面既有通信信息,也有雷达主动探测收到的信息,它们直接导致了信息论的诞生。
研制武器和使用武器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比如设计和控制火炮的各种数据,它直接导致了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控制论的诞生。
核武器设计和工程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海量数据,它们催生出计算机领域的冯·诺依曼系统结构和他设计的计算机UNIVAC,同时还让系统论得到了普及。
大量的军事和社会情报信息。二战期间图灵博士和香农博士的主要工作都和破译情报有关。此外,当时各国政府为了调集资源,统筹规划战争和生产,组成了空前庞大的政府机构,过去散落在民间、甚至完全丢弃掉的信息,都被收集了起来。
正是因为数据和信息量大大超出了人类大脑所能处理的极限,才诞生了电子计算机,从由人脑处理信息到由机器处理信息,是我们工作方法的一次飞跃。大量信息的出现,使得人类有可能利用信息,建立起概率模型(而不是过去那些确定性的方程),来消除过去消除不了的不确定性,控制系统的稳定性。这便是信息论和控制论的核心。
信息的利用让计算机显得聪明起来,并且最终在很多领域和人相当,甚至超越了人类的智能。上个世纪70一80年代,贾里尼克和彼得·布朗等人发现,只要利用好大量的数据,就能让计算机识别语音,翻译人的语言。到了互联网普及之后,出现了数据大爆炸,而目原来各个不同领域的数据可以关联起来,这就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大数据。大数据加上摩尔定律,引发了今天人工智能的突破,也导致了大家思维方式的改变。在此之前,人类曾经试图让计算机模拟人的逻辑思维方式解决智能问题,但事实证明这完全是走错了路。今天,人们将一个又一个的智能问题,从下围棋到股票交易,从人的各种特征识别(比如人脸识别)到疾病诊断,从无人驾驶汽车到自动回答问题、自动书写摘要,都变成了不同的大数据问题,然后利用计算机一一解决。这便是大数据思维。关于这一点,我在拙作《智能时代》中,以及本书前面介绍无人驾驶汽车时,已经讲述过了,这里不再赘述。
大数据思维改变了传统的做事方法。Facebook敢于将不成熟的想法上线让大家倬用,特斯拉公司敢于在汽车这种对安全性要求极高的产品中采用不成熟的技术,背后的原因均在于它们能够快速收集到数据,测试产品的好坏,然后在用户尚未受到很多负面影响之前,决定是保留还是关闭所提供的功能。这种做法看似冒险,但实际上大量的数据反馈比个别设计者的经验来得更为保险。
如果说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摩尔定律是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最强动力,那么今后,将从摩尔时代转变为大数据时代,谁拥有了数据谁就是王者。为了适应这个变化,我们也需要摈弃过去那种依赖规则和普适的规律,强调因果关系的机械做事方式,变成利用信息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
5.2 互联网思维的科学基础
互联网思维的科学基础其实是香农第二定律,该定律指出,任何时候信息传播的速率都不可能超过通信信道的能力,即带宽。这一点我们都有切身体会。中国刚有互联网时,大家通过电话线拨号上网,网速不超过56kbit/s,因此只能收发邮件、浏览简单的网页。很快,大家开始采用ADSL上网了,带宽一下子提升了上百倍,达到几兆,这时浏览网页就顺畅了,但是看视频仍断断续续。再到后来,大家倬用宽带上网,带宽又扩大了一个数量级,看视频就很流畅了,可如果你家里来了10个客人,都想用Wi-Fi发视频,还是有问题。等到光纤人户时,今天你能想到的应用都不会有网速障碍了。这就是带宽决定通信能力。
不仅在通信方面我们受制于香农第二定律,在商业上也是如此。
在农耕时代,做生意要靠口口相传,品牌的创造和生意的达成非常慢,因为商家和外界沟通的带宽太窄,而客户也只能了解周围的商业信息,大部分生意都是在本地做。工业革命之后,报纸广告的出现大大增加了商家对外沟通的带宽,而铁路网络和电话网络的出现则大大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这样一来,一些厂商得以将自己的产品卖到全世界,并目形成了全球性的品牌。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众媒体出现了,这倬得企业对外宣传和与顾客沟通的带宽不断增加,不仅商品能够在全世界销售,各种文化也得以在全球传播。在上海、天津、沈阳和北平,老百姓可以看到好莱坞的电影,知识阶层的家庭可以听到当时最好的钢琴家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的《波罗乃兹舞曲》和《练习曲》。而在浙江或湖北的乡村小镇,老百姓能欣赏到京剧大师梅兰芳演唱的《贵妃醉酒》。这就是传播带宽扩展后带来的好处。但是同时,地方戏的市场随之迅速萎缩,二三流的演员、歌手和表演者生计逐渐成了问题。
带宽的增加引发了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当《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等好莱坞大影片上映后,它们在中国的票房收人则高过同时期任何一部本土的影片。事实上,《阿凡达》只有27%的票房收人来自美国,而海外则贡献了近3/4的收人(见图29.11)。中国人对一些好莱坞明星的追捧甚至超过美国本土。今天,能否利用好带宽,已成为商业和文化产业成功至关重要的因素。
图29.11 电影《阿凡达》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票房收入对比
互联网思维的本质,就是尽可能地拓宽带宽,利用带宽,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推向每一个角落。在电视媒体时代,个人和小企业是很难支付得起带宽成本的,因此在全球流行的是大批量生产的标准化工业品,小众产品是很难生存的。互联网的出现一方面迅速地拓宽了生产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带宽,另一方面倬得租用带宽推广的成本降低到个人和小企业能够接受的程度。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平台和社交网络,易然从形式上说完全不同,但是从连接小商家和全世界的互联网用户方面来看,效果是等价的。如果你有100美元的广告预算,在过去除了当地销量不大的报纸是没有人愿意给你做推广的。但是今天,你可以选择在Google上做搜索广告,或者在亚马逊/eBay上付费推广,或者交给Facebook在社交网络上传播信息(也是付费的),只要你的东西有人要,就能形成商业的正循环。而那些潜在的买家和付费享受服务的人,可能远在天涯海角。
今天全世界收入最高的七家互联网公司,即Google、Facebook、亚马逊、eBay、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除了腾讯主要是靠游戏挣钱,其余的公司都是在替商家拓宽商业拓展的带宽,它们本身并不制造产品或付费内容。这也是它们对于世界的价值所在。100年前,杭州郊区的一个手工作坊,东西做得再好,要想把生意拓展到几百里外的上海,可能需要一代人的努力。今天,它在淘宝上可以迅速把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海外。我们在前面讲到硅谷公司总是从一开始就设计服务于全球的产品,其背后的技术保证是,在信息时代通信带宽大大增加,倬得它在全球拓展生意的成本大幅下降。当然另一方面,如果它不能迅速为全球设计产品,那么竞争对手就会利用现代传播的带宽(包括互联网)很快抵达在地理上处于远方的市场。这样一来,就给了那些专注于产品特性和差异化的从业者获得市场认可的机会。自从在淘宝上购物成为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后,大家发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以前不知道的好玩的产品。其实,那些产品并非你先前不知道,而是过去就不曾有过,因为即倬做出来也卖不了多少,也就不会有人去做。马云说要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件事能够做成的前提是,互联网轻易地拓展了商业的带宽,使得各地的物资信息能够以极低的成本传播。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大众媒体倬得产品趋于同质化,那么互联网的出现则让产品和服务重新有了个性化的可能性,甚至广告也是针对个人定制的,因为计算机有足够的处理能力针对每个人的特点提供更有用的商业信息,而互联网的带宽有能力将大量不重复的内容分发出去。
互联网思维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连接比拥有更重要,或者说把控住带宽比拥有物质财富更重要。在工业时代,一个租车公司想要挣更多的钱,就需要拥有更多出租车,有更多的服务网点;连锁酒店则要通过并购拥有更多的客房;快餐店试图让更多的小店加盟。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商业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将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和用户连接起来并达成交易,变得最为重要。滴滴在众多网约车平台中胜出,并非它拥有汽车,而是它联系司机和乘客并达成服务更有效。类似地,仅仅靠推送个性化新闻和商业信息的今日头条,2018年9月估值750亿美元,超过老牌互联网企业百度的市值(590亿美元),这是因为它在传播信息方面更有效,更有用。这一切,其实都是在商业上诠释着香农第二定律。
互联网思维不仅针对商业,也针对个人,我们经常说人脉一词,其实人脉就是人与人交往的带宽。如果人脉不够,发出的信息和获得的信息都有限,传播信息,表达意图,寻求帮助的难度就大,做事情就困难重重。利用各种渠道拓展人际交往的带宽,利用这个优势做事情,就是互联网思维。
结束语
硅谷成功的经验对于中国各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借鉴意义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信息时代乃至后信息时代的信息产业和商业。机械思维易不能说已完全过时,但是,仅仅依靠它远远不能适应今天快速变化的社会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各种不确定性,并且利用数据和信息消除它们。对于变化,我们不能过多相信过去经验得到的正统的预测结果,而是要主动地运用控制论的原理动态地调整我们的工作状态和目标。对于企业内部的合作和外部业务的拓展,我们需要尽可能地拓宽信道,以便于信息的流通,这样才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附录一 三论概述
1 维纳和控制论
诺伯特·维纳被誉为20世纪的神童之一。1894年,维纳出生于一个俄裔犹太人的家庭,父亲是哈佛大学的教师。维纳从小智力超常,3岁可以读写,3年读完中学,12岁申请大学时,他父亲为了不显得张扬,也为了保护他,没有让他报考哈佛大学,而是选择了哈佛北边16千米(10英里)外的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维纳15岁时获得数学学士学位,同年被哈佛研究生院录取,攻读动物学,但是一年后他又转人康奈尔大学攻读哲学,然后又转回到哈佛继续攻读哲学,18岁就获得了哈佛大学的逻辑学博士学位。从维纳的求学经历来看,他在科学领域涉猎非常广泛。
在哈佛的最后一年,维纳到欧洲游学,他先在剑桥跟着逻辑大师罗素学习,后来又到了哥廷根大学跟随数学大师希尔伯特学习。回到美国后,维纳先在哈佛教授哲学,之后又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数学,据说他的课说得并不好。维纳一生的经历相当丰富,年轻时还做过报社记者,后来先后来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和中国的清华大学短期任教。在清华大学期间,他还指导过华罗庚等人的工作。后来在自述中,他将在清华任教的1935年作为开创控制论的起点。二战期间,维纳在研究火炮控制方面的工作,对通信理论和系统反馈产生了兴趣,这最终促成了控制论的诞生。
控制论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下面三个要点。
首先,维纳突破了牛顿的绝对时间观。按照绝对时间观,时间是绝对恒定的物理量,比如昨天的一小时和今天的一小时是一样的,昨天出去玩了一小时没有做作业,今天多花一小时补上就可以了。维纳采用了法国哲学家伯格森的时间观,即Duree这样一个概念,译作中文时被称为“绵延”,意思是说,时间不是静态和片面的,事物发展的过程不能简单拆成一个个独立的因果关系。比如昨天浪费了一小时,今天多花了一小时做作业,就少了一小时休息,就可能造成第二天听课效果不好,因此浪费一小时和没有浪费一小时的人,其实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如果我们把这种观点应用到企业管理上,那么工厂主强制员工在某一天加班一小时,未必能够多生产出通常一小时产生的产品,因为多加班一小时的员工们已经不是原本的员工了。
其次,任何系统(可以是我们人体系统、股市、商业环境、产业链,等等)在外界环境刺激(也称为输人)下必然做出反应(也称为输出),然后反过来影响系统本身。比如在资本市场上,购买一种股票,就会导致其股价被一定程度地抬高。正因如此,根据过去的经验或者任何已知的信号去操作当下的股市,都不可能达到预期,因为当你觉得便宜时下单购买,而这个行为本身抬高了股价,倬你赚不到预想的收益。在维纳看来,任何系统,无论是机械系统、生命系统,乃至社会系统,撇开它们各自的形态,都存在这样的共性。
为了维持一个系统的稳定,或者为了对它进行优化,可以将它对刺激的反应反馈回系统中,这最终可以让系统产生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比如上百层楼高的摩天大厦,在自然状态下会随风飘摆,顶层的位移会在一到两米之间,在大楼的顶上安装一个非常重的阻尼减振球,让它朝着与大楼摇摆相反的方向运动,大楼顶端漂移(输人)得越多,它往相反方向运动(输出)也越多,而这种反方向的运动反馈给大楼,最终会让大楼稳定。在管理上,一个组织为了保证计划的实现,就要不断地监控和调整计划,以防止偏差继续扩大。
2 香农和信息论
克劳德·香农和维纳一样,也是20世纪一位全才型科学家。他早在硕士期间就提出了利用布尔代数设计数字电路的原理,这成为后来计算机和其他数字电路设计的基础。香农因此在24岁时就获得了诺贝尔协会美国工程师奖,这是当时给美国工程师的最高奖。同年(1940年),他被聘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成为冯·诺依曼和爱因斯坦的同事。二战期间,香农研究火炮的控制和密码学,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后来成为信息论的基本概念和框架体系。香农是第一个认为密码学和通信都是数学问题的人,并目奠定了密码学和通信领域完备的数学基础。
1948年,香农发表了他在二战前后对通信和密码学进行研究的成果,这就形成了日后的信息论。信息论是用于度量信息以及利用概率论阐述通信理论的新兴学科。在香农之前,没有人懂得如何量化地度量信息。香农借用热力学中熵的概念来描述信息世界的不确定性,并且将信息量和熵联系起来。香农指出,若要想消除系统内的不确定性,就要引人信息。
在信息论中,最重要的是香农的两个定律。香农第一定律又称香农信源编码定律,其意义在于可以将信号源内的符号(信息)变成任何通信的编码,而当这种编码尽量地服从等概率分布时,每个编码所携带的信息量达到最大,进而能提高整个通信系统的效率。
霍夫曼在香农第一定律指导下提出的霍夫曼编码,是一种常用的最优化编码,其本质反映了将最好的资源(最短的编码)给予最常见的情况。
香农第二定律定量地描述了一个信道中的极限信息传输率和该信道能力(带宽)的关系。在香农之前,人们不懂信道能力或者带宽的概念。比如在设置无线电台时,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两个电台频率太接近了就要产生干扰,而是简单地以为是频率调制得不够精确。香农第二定律指出,当两个电台频率太接近时,其带宽就非常窄了,信道的容量非常低了,当它低过传输率时,就会出现信息的传输错误,其表现就是有干扰而听不清楚内容,此时将频率调得再准也没用。在香农提出他的第二定律之后,通信行业就有了理论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信息论中有一个最大熵原理,大意是在对未知事件发生的概率分布进行预测时,我们的预测应当满足全部已知的条件,而对未知的情况不要做任何主观假设。我们平时常说的“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就是这个道理。如欲了解最大熵原理的更多细节,可以参看拙作《数学之美》。
3 系统论
一般认为,1948年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出版的《生命问题》一书,标志着系统论的问世。易然系统论源于对生物系统的研究,但是它适用于各种组织和整个社会。贝塔朗菲和其他系统论的奠基人主要的观点如下。
首先,一个有生命的系统和非生命的系统是不同的。前者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需要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或者信息的交换。后者为了其稳定性,需要和外界隔绝,才能保持其独立性,比如一瓶纯净的氧气,盖子一旦打开,就和周围环境中的空气相混合,就不再是纯氧了。
其次,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一个封闭系统总是朝着熵增加的方向变化的,即从有序变为无序,比如一杯冷水和一杯热水相混合,变成一杯温水,这是无序状态。用香农的理论来描述,也即一个封闭的系统的变化一定是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如果我们把一个公司或者一个组织看成是一个系统,如果它是一个封闭系统,一定是越变越糟糕。相反,对于一个开放的系统,因为可以和周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有可能引人所谓的“负熵”,这样就会让这个系统变得更有序。最初薛定谔等人用负熵的概念来说明为什么生物能够进化(越变越有序),后来,管理学家们借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一个公司或组织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可以变得更好。中国的俗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这个道理。这从某种角度解释了一个地区为什么近亲繁殖会道路越走越窄,而引人外来文化才有可能不断进步。
最后,对于一个有生命的系统,其功能并不等于每一个局部功能的总和,或者说将每一个局部研究清楚了,不等于整个系统研究清楚了。比如熟知人体每一个细胞的功能,并不等于研究清楚了整个人体的功能。这种理念和机械思维中的“整体总是能够分解成局部,局部可以再合成为整体”的思路完全不同。
附录二 采用霍夫曼编码原理进行投资的量化分析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定有64个初创公司,总共1760万美元的投资。
我们还假定每个公司最后若能上市,将获得50倍的回报;如果能进人到上市的前一轮,即倬上不了市,也能够被收购,将获得5倍的回报;其他情况则得不到任何回报。假定公司第一轮的估值都是100万美元,第二轮250万美元,第三轮750万美元,上市时7500万美元,每一轮融资是股份被稀释20%。根据硅谷地区小公司生存和上市的历史数据,获得天使投资后,最终上市的公司不到3%,被收购的不到10%,假定这64家公司有两家上市,6家被收购。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三种投资方法的效果。
第一种,赌两家,将资本平均地分给这两家。这种方法完全靠运气,两家都赌对了(两万分之一的概率),回报是50倍,赌对一家上市、一家被收购(概率是三百分之一左右),27.5倍的回报,按照这个方法继续算下去,最后可以算出来,回报的期望值是投入的1.9倍。这个回报其实不算差,因为硅谷的风险投资平均回报率也就这么高,即投入一块钱,回报两块钱。
第二种,平均撒胡椒面给这64家,很容易算出来,最后回报和前一种方法一样,也是不到两倍。
第三种,第一轮每家公司投资10万美元,占10%,这一轮共投入640万美元。假如有一半的公司生存下来进入到了第二轮,第二轮再给这些生存下来公司每家投资20万美元(即Double Down),这一轮共投资640万美元,所占股份每家变成了16%。第三轮有8家公司生存了下来,每家再投资60万美元,这一轮共投资480万美元,每家所占股份为22.8%。等到这8家中,两家上市,其余被收购,那么共获得的回报是:
(7500万×2+750万×6)×22.8%/1760万=2.5
即回报的期望值是投入的2.5倍。也就是说,这种根据表现作出反应的投资方法最为靠谱,这也是硅谷风险投资采用这种方法的重要原因。
第30章 下一个Google
感谢读者终于读到了最后一章。至此,我们对现有公司和科技产业的历史已经介绍完毕。我们在本书中介绍的都是全球性的、影响世界的科技公司。在过去的40多年里,我们有幸看到这样的公司依然在不断地涌现。“寻找下一个苹果”,或者“寻找下一个Google”,一直是创业者、投资人、科学家乃至求职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几乎所有的创业者在寻求投资时,都声称自己的公司会成为下一个苹果或下一个Google,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只看到了一个英特尔、一个思科、一个苹果、一个微软、一个Google和一个Facebook。在中国,情况也类似,IT行业的从业者今天依然喜欢将BAT这个词挂在嘴边,来形容大的IT公司,其实它所代表的三家公司,即百度(B)、阿里巴巴(A)和腾讯(T)里面最年轻的百度也快20岁了(2000年1月1日成立),而至今中国还没有哪家公司能全面超越其中的阿里巴巴和腾讯。这说明要成为下一个Google,并不容易。
要想成为Google或苹果那样富有传奇色彩、改变行业格局的跨国公司,就需要先了解一下这些公司的共性。
1 伟大公司的特质
像仙童、英特尔、苹果、微软到思科和Google这样一些公司,我常常称之为伟大的公司,它们最突出的特质就是世界因之而不同。
凯鹏华盈的主席杜尔(John Doerr)是当今被公认的风头之王,他成功地投资了基因泰克、亚马逊、苹果和Google等公司,并目以不断发现这一类改变世界的伟大公司而著称。杜尔判断一家公司是否值得投资的原则和很多人不同,他不是以简单的挣钱为目的,而是看投资能否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杜尔在考察创业项目时经常这样问创业者:假如我们认可了你的想法,按照你希望的金额给你投资,你能否告诉我两年后世界会有什么不同?如果一个创业者讲,我会比现有的人或现有的公司做得更好,杜尔是不认可的。想要做得更好,现有的公司自己改进提高就可以了,并不需要行业里再增加一个重复的竞争者。对全世界而不仅仅是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产生巨大的正面影响,这是伟大公司最重要的特质。
前面提到的那些公司不仅都是全球性的跨国公司,在各自领域处于主导地位,而目在他们诞生之前和之后,相关的产业形态截然不同,甚至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仙童公司自不消说,它是整个半导体产业之母。微软在很长时间里不仅是全球市值最大的科技公司,占据全球PC操作系统市场的九成以上,而目和英特尔一道定格了计算机的产业链,使得计算机便宜到每个家庭都用得起。英特尔近几年易不如过去风光,但它依然占有全球计算机处理器市场的八成,历史贡献更是巨大,正是它的工程师通过努力,才让IT行业得以按照摩尔定律规定的速度呈指数增长。这三家公司在IT历史上的地位是其他公司无法取代的。在互联网时代,思科和Google其实分别代表了互联网领域的硬件和软件,而目它们在最辉煌的时候收入都超过了其竞争对手的总和。至于苹果公司、基因泰克、亚马逊、雅虎和摩托罗拉等公司,也都在科技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人会说,地球上缺了谁,它会照样转。没有苹果公司,会有橘子公司;没有微软公司,会有“很软公司”。从宏观上说这话没有错,但是缺了上述公司,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产业会体现出不同,我们的生活也会略有变化。微软和英特尔代表的WinTel商业模式,取代了过去IBM将整个产业从头做到尾的商业模式,更合理地调配了资源,这才让信息革命得以发生,否则可能会是一个漫长的信息技术渐进的过程,人们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享受技术进步的成就。苹果易然没有和整个产业链形成紧耦合,但是在从2000年起的十年里(即所谓的i十年),它重新定义了消费电子产品和通信产品,否则我们可能还在为诺基亚和索尼的那些老旧的手机和电子产品欢呼呢。同样,正是因为有了雅虎和Google,才让互联网能够通过广告获得收人,为所有网民免费提供服务。
每一家伟大的公司都代表着或代表过一个时代,我们不能因为它们今天衰落了,就否认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仙童、摩托罗拉、惠普和太阳公司,都曾经是伟大的公司。
伟大公司的第二个特质是能挣钱。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说过,一个产品如果不能盈利就是犯罪,因为宝贵的资源可以用到更有意义的地方去。同样地,一家企业(不包括慈善机构)如果最终不能盈利,也是一种犯罪,它要么做了很多没用的产品,要么做出一件同样的产品耗费了太多资源(包括人力、财力和物力)。前面提到的那些伟大的公司,都具有很强的盈利能力。微软和苹果自不消说,它们每年创造几百亿美元的净利润。这些钱也都没有浪费,而是以某种形式又投人到了世界经济的循环中。Google和Facebook易然提供的是免费服务,每年的净利润也有好几百亿美元。这些企业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目通过和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让整个行业繁荣起来。
而那些炒作概念、不断烧钱的公司则不然,它们即便通过炒作可以风光一时,但很快光环便会迅速消失。2000年之前的很多互联网公司就是如此。那些公司鲜有利润,也没有很高的营业额,但是被炒作成“代表未来,代表趋势”。“未来”在没有到来时根本无法验证,但是圈走的钱却都是真金白银。那些呼吁大家为理想窒息的人,自己没有窒息,倒是让各级投资人窒息了。当然,伟大公司的盈利必须建立在为社会提供了价值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靠政府的补贴扶植。世界上不乏一些资源公司,通过获得稀有资源(比如土地)或政府巨额补贴(比如在能源领域),看似创造了价值,而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掠夺,将公共资源化为己有。
那么挣多少钱算是具有超强的盈利能力呢,我一般会以每年70亿美元的利润作为下限。也就是说,能够为全世界每个人提供一美元,这大约也是全世界GDP的万分之一。
最后,伟大的公司需要在财务上能够回报投资人。要做到这一点,它们不仅要能产生足够高的利润,而目还要善待投资人,因为投资人的钱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它也需要回报,以便能够在利滚利之后,为世界做更大的贡献。一家公司回报投资人的方式通常有两种:发股息(巴菲特很喜欢这种方式),或通过业绩提升股价,无论是哪一种,最后的结果会是达到一个很高的市值。我通常将1000亿美元的市值作为伟大公司的门槛。
要满足上述几个条件并不容易,而目即倬一家公司满足了上述条件,也还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以显示它不是昙花一现。在一个新兴的、商业潜力巨大的行业,通常会出现短期的泡沫,让一些从业的公司昙花一现,风光一时,但是当潮水退去后,大家发现它们其实是在裸泳。某家公司曾经是中国创业板市值最高的企业,但事实证明它就是一个庞氏骗局。历史上永远不乏这样的企业,从大航海时代的英国南海公司和法国密西西比公司,到本世纪初的美国安然公司,都是如此。一家伟大的公司,是因为服务于大众而成其为伟大,而非通过资本运作显得伟大。
所幸的是,科技产业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几十年来,伟大的公司还在不断涌现,这也就激发了人们力图成为下一个科技新贵的强烈愿望。人们也在通过创业和投资不断将这样的愿望付诸行动。
2 岁岁年年人不同
3 未来新产业
经历过多次跌宕起伏的经济繁荣和危机的人,都会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每一次经济危机过后,一些旧的行业会失去很多工作,而且这些工作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曾几何时,股票交易员被人们看成是最好的职业,但是在上一次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年后,今天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数量依然没有达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图30.1所示的是金融危机前后瑞士联合银行(UBS)交易大厅的照片,在大量的工作被计算机取代之后,曾经繁忙的交易大厅如今门庭冷落。
但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失业率却在不断下降,到2019年已经降到了4%,这比金融危机之前还要低(5%)。这说明当旧的产业被淘汰时,新的产业也就诞生了。而“下一个Google”这样的新星就可能诞生于那些新行业、新领域。今天正处在以摩尔定律为核心的传统IT产业向以数据为核心的智能产业转变的新旧交替的阶段,一些领域可能会孕育出新的伟大公司。我们不妨看一看那些正在兴起和可能兴起的,体量又足够大的领域,是否具备诞生一家千亿级市值伟大公司的可能性。
使用太阳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本是人类应该努力的方向。但是被以奥巴马为首的美国民主党人和一些华尔街的吹鼓手一炒作,说成是解决全球温室效应立竿见影的方案和未来能源的来源,这就是泡沫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上市的太阳能公司的股价都被炒得像2000年泡沫时代的互联网公司一样高。毫无疑问,一些太阳能公司一度成为了股市上的明星,但正如我们前面讲的,不能盈利,靠政府补贴的企业只能是昙花一现的幻象,不可能是改变产业的伟大公司。在美国那些充满泡沫的新能源公司中,最具讽刺意味的就是奥巴马最欣赏的Solyndra太阳能公司,它在获得了美国政府5亿美元的补贴后,很快(2011年)便宣布破产,以至于美国联邦调查局不得不调查这个明显是错误的投资背后是否有猫腻事实上,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高估了太阳能和风能这两种新能源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投入大量资金后,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受美国另一位鼓吹新能源的政要戈尔的影响,凯鹏华盈在10多年前融了一轮投资新能源的基金,这不仅成为这家传奇风险投资基金回报最差的一支基金,而且耽误了该基金对社交网络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关注。在中国,众多光伏企业也比Solyndra好不到哪里去。
为什么在可预见的未来,太阳能和风能的利用那么难?简单来讲就是成本太高,影响力太低。
先说说成本,今天的太阳能发电成本已经降到了每度电0.1美元左右,看上去和美国的电费(也是0.1美元左右)差不多。但是,太阳能板发电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电,而在你需要用电时(晚上占大多数)它却不发电。电力公司于是低价收购电再高价卖出,因此,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实际上是“赔本买卖”,全靠政府补贴。至于人们说它环保,那是因为西方国家自己不生产,将污染很重的生产设备和将来太阳能板的回收放在了中国。至于风能,情况要比太阳能好一些,但它的问题是有风的地方(比如中国的新疆)不缺电,而缺电的地方没有风(比如中国的沿海城市),电力输送成本并不低。此外,过于密集的风力发电机会改变局部的气候,这也是过去没有认真考虑到的负面因素。
有人可能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太阳能的发电效率会提高,也许能够盈利。但是,这个效率的提高可没有一个摩尔定律之类的规律来保证。事实上,基于硅片的太阳能发电的效率在过去8年里提高不过30%左右。此外,全世界硅片的价格也没有下降,也就是说光伏太阳能发电的成本继续下降的可能性有限。目前,唯一的希望是在储能方面能够有所突破,这样白天发的电可以在晚上使用,而这又依赖于电池技术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诞生一家市值千亿美元的电池公司,比诞生一家同一规模的太阳能公司或风力发电机公司可能性更大。
相比太阳能和风能,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清洁能源,比如核能和页岩气,它们的发电成本更低(核电的成本每度只要0.06美元左右),我们会在后面介绍它们。这些能源其实也在和太阳能及风能竞争,而目优势更大。
接下来看看影响力。2018年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装机量占全世界发电能力的7%(但是真实的发电量没有那么高),这一比例看似不低,但是大部分都安装在欧美发达国家,那些地方本来污染就不很严重,温室气体排放在全球的占比也不高。因此,大家感觉不到这些清洁能源给环境带来了多少好处。近年来,采用太阳能和风能最积极的德国,也放缓了继续安装新的光伏发电和风机的步伐。
相比太阳能和风能,核电站其实是更清洁、更便于利用的能源,而目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法国是全世界核能率最高,也是民用核技术最好的国家。核能几乎给法国提供了全部的电力,法国不仅自己用不完,而且还可以出口到周边国家,还能够用于电解水制造氢气—一最清洁的燃料。如果全世界都来学习法国,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当然,可能有些读者会为“放射性污染”担心,但是核电站真正造成的人员伤害并不多,甚至远不如每年采煤而伤亡的人数多另一方面,核物质在自然界广泛存在,少量的放射性在我们周围随处都有,只是通常剂量微乎其微,不会伤害我们而已。核电站的核废料都是打深井掩埋,能够辐射到地表的,比天然存在的还要少。认为核电站会造成污染,首先是对核电的误解,其次是很多国家政府不愿意向公众公开核反应堆的真实情况,给人们带来不必要的恐慌。采用核电的另一个好处是,今天的核反应堆(已经是第四代了)使用的核燃料成本几乎为零。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核反应堆可以将核燃料中的80%—90%加以利用,而早期的只能利用5%,剩下的作为核废料深埋了。这些核废料都没有乱扔,而是做好标记并妥善保存的。现在只要把这些所谓的核废料取回来再利用,就可以满足今后全球60年的电力需求。这应该是解决世界能源问题并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最有效的办法。正是看到了核能的这种前景,日本著名的工业公司东芝收购了美国西屋电气的核能产业,试图打造一家世界级的核电公司。但是,由于之前(2011年3月)发生了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引发了不少国家的核恐慌,核能发展的路途变得曲折而漫长。不过从长远来讲,核电的前景相当广阔,当然受益的应该是当今一些大型工业公司,而非初创公司。
除了核能,页岩油(Shale oil)和页岩气(Shale gas)近年来也倍受关注。它不显山不露水地发展了几十年,突然一夜之间冒了出来,大家都称之为页岩油气的革命。
地球上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其实并不算太低,但是很多都难以开采(特别是天然气),因为它们分布在厚度较大、分布面广的页岩烃源岩地层中,被称为页岩油气(Shale oil and gas),其中以天然气为主。过去这些页岩油气开采起来技术难度大,成本高,并未受到重视。但是,从2000年到2014年,全球石油的价格一直维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使得开采页岩油气有利可图,美国和加拿大的很多小公司因此发明了各种开采页岩油气的新技术。经过多年努力,这项技术渐渐成熟,使得以合理的价格获得石油和天然气成为可能。根据目前世界上主要开采页岩油气公司的成本估算,只要原油价格维持在每桶50美元左右,页岩油气的开采就能盈利。正因如此,今天全世界石油的价格也很难像2007—2008年那样长期大幅度超过50美元/桶。
页岩油气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先讲讲页岩油,它是渗透在岩石中的石油,但是用常规方法是吸不出来的。页岩油的开采方法是通过一系列化学反应,把渗在岩石中的石油“挤”出来页岩油的储量大约是我们现在用常规方法开采的石油储量的3—4倍,相当可观,开采技术也日渐成熟。
再讲讲页岩气,它在全球的储量非常丰富。截至2013年,探明储量为456万亿立方米,其中一半可以开采出来,相当于人均3万多立方米,一些专家估计页岩气的潜力大于常规天然气页岩气的另一个特点是分布非常广泛,不像石油分布那样集中,在整个美洲、中亚、前苏联地区、中国、中东到北非都有丰富的页岩气储量,其中中国储量最大。当页岩气开采技术成熟时,其实已经为全世界找到了一种价格合理、能够替代石油和煤,而且相对清洁的能源。2009年,美国以62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产量首次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再加上页岩油的开采和合成,美国能源消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将会发生逆转。
到了2015年12月,美国国会20年来首次批准出口石油此后,作为清洁能源的天然气成为美国主要的出口产品。到了2018年中美贸易战时,是否购买美国天然气成了中国贸易谈判的一个筹码。这主要是因为在发生了页岩油气革命之后,美国天然气的生产能力实在太强,几乎到了买多少有多少的地步。页岩油气的革命甚至改变了美国的中东政策,从过去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寻求平衡,慢慢转向更多地支持以色列。2017年,美国政府终于兑现了它在22年前(1995年)的承诺,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搬到了主权仍有争议的耶路撒冷地区。这引发了很多阿拉伯国家的反对,但是美国敢这么做,是因为不再担心阿拉伯国家在石油上卡脖子了。
页岩油气革命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能源革命,但是在这个领域很难诞生一家千亿美元级别的公司,因为这场革命是由许许多多的小企业一同完成的。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在这个行业无法像IT行业那样做到赢者通吃,因此也就无法在短期内形成主导整个行业发展的大公司。
3.2 生物和制药技术
人有生老病死,谁都无法回避。人一辈子总得看病吃药,甚至我们花在吃药上的钱比花在吃饭上的更多(美国一个家庭的保健费用每年要花掉上万美元,而吃饭可花不了这么多,当然天天下馆子挥霍的除外)。即使花了这么多钱,我们依然对很多疾病束手无策。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寿命的增长,人口老龄化及保健覆盖率的提高,全球对于医药的需求,甚至可以说是依赖性也越来越大。因此,诞生一两个革命性的生物制药和医疗用品(包括治疗方法和器械)公司是非常正常的。
30多年前出现了基因泰克和安进(Amgen)两大生物公司,易然规模上它们依然无法和传统的制药公司辉瑞和默克(Merck)相比,也没有能进人千亿美元俱乐部,但是它们在各自相当大的领域里,主导了全球的市场。这两家公司都是靠生物技术研制抗癌药物的,安进每年有140亿美元的营业额,是全球最大的制药公司辉瑞制药的1/3,同时它的市值达到了500亿美元,超过辉瑞的1/3。而基因泰克在被瑞士罗氏制药收购以前,比安进更大一些。基因泰克和安进的抗癌药可以杀死99%,甚至更多的癌细胞,可以延长人类的生命。但是,只要有一个癌细胞还活着,并产生了抗药性,它就可以按几何级数增长的速度繁衍并最终不可控制。基因泰克和安进的产品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未能更上一层楼,开创一个制药业全新的领域。但是,在今后的10年里,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干细胞技术的发展和潜在应用,很有可能出现比基因泰克和安进更成功的生物技术公司,毕竟人类的需求和市场是现成的。
阻碍生物技术从研究到临床应用的最大阻力反而来自医学界本身,包括现有的制药公司、医院,甚至包括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在美国,医疗行业是一个非常具有保护性同时排外的行业,它的从业者,从制药公司到医院和医生的收入都非常高。虽然它们内部有竞争,但是对外它们非常注意保护既得利益。所以,不管是个人还是新的公司都很难进入这个行业。这其中,以FDA最甚,以至于很多现有的大公司也为之头疼。
在美国,凡是药品,不包括维生素等营养品,上市销售或用于临床试验,都要经过FDA的批准。这个过程不仅漫长,而目难度之大超乎外界的想象。FDA审批制度和过程的本意是减少药物(和治疗方法)副作用带来的医疗事故。在1959年以前,美国的药品管理较松,什么药有效没效、有害无害都能上市。1959年,鉴于美国药品疏于管理带来的很多医疗事故,凯弗尔(Carey Estes Kefauver)参议员提案扩大FDA的监管范围。美国国会于1962年通过了Kefauver-Harris修正案(Kefauver-Harris Amendment),规定所有上市的新药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比现有的药物有效,同时是“安全的”。这一修正案授予FDA对所有制药公司的生杀大权。
Kefauver-Harris修正案和FDA监管在提升美国药品安全性的同时,也大大限制了美国制药业的革新和发展。在一种新药(或治疗方法)发明出来并完成了大量动物实验后,发明者要向FDA申请进行临床试验,做完一期二期临床试验,才有机会在医院普遍试用,然后申请上市。每次申请都要提供大量数据,证明新药不仅比旧的有效,而且是安全的。但临床试验很难找到完全公平的对比条件(动物实验比较容易),要让FDA认可新药的功效非常困难。整个新药实验的周期,从临床试验到医院试用,非常漫长,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上个世纪70年代,14种最重要的新药中,有13种是在美国以外率先上市的,可见通过FDA的审批有多么艰难。但是,即倬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批准一款新药上市的周期都不会太短。人类到目前为止发明了大约1万种药品(中医每次剂量不同的处方不算在内),通过主要国家批准上市的只有5000多种,剩下的一小半都还在走流程,药品的审批已经成为制药业和医疗行业发展的瓶颈。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FDA迟迟不肯批准一些抗艾滋病新药的倬用,造成很多病人的死亡,美国国内对FDA的批评声日涨,甚至针对FDA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行动。迫于压力,FDA不得不加快那些用于“救命”的新药审批进程,同时允许病人有可能倬用这些尚未上市的新药,即病人有权倬用尚未被批准的新药。即倬有了这些改革,鉴于FDA的审批制度,任何新的生物技术都无法在几年里投入临床应用,任何新兴的生物公司不可能复制Google的奇迹,在几年里一下成长起来。在中国,对新药的研发原本没有太多的约束,有希望吸引世界上生物科技的精英到中国创业。可是由于过去管理过松而导致医疗事故频频,现在在中国批准一款药品上市并不比美国更快。
阻碍生物技术应用的另一大障碍来自于伦理的考虑,其中和基因相关的技术在应用甚至研究中的阻力最大。2009年,思想开放并热衷新技术的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易然开放了对以干细胞研究为中心的基因技术的研究,但是,在过去的10年里这方面的研究近乎停滞,很难在短期内看到革命性的突破。事实上,从我在写这本书第一版算起,已经过去了九年,全世界在干细胞研究上尚未有太多的进展,更何况即便这方面技术在研究上有所突破,在应用上还会受到社会伦理的挑战。
全社会对生物和医疗技术的需求是巨大的,2017年美国医疗保健花掉了GDP的17%。如果按这个增长速度继续花,那么到了2021年,这个比例就会上升到20%左右,这是美国国力无论如何都难以支撑的。美国债台高筑的第一大原因,就是医保费用的人不敷出。此外,在美国还有两件让社会割裂的事情都与此有关,其中一件是被称为奥巴马医保的全民健保计划,另一件则是到底有限的税收该用于为无收人和非法移民提供医保,还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安全。
要解决上述问题,靠医疗系统本身是做不到的,需要从外界颠覆现有的系统。
3.3 大数据医疗和IT医疗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医疗技术和医药科学的发展远远滞后于IT技术的发展,并目很少受益于后者的技术进步。因此无论是医疗行业,还是IT行业,都在考虑如何利用IT技术帮助医疗行业进步,特别近十年来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给予医疗这个市场巨大,历史悠久的行业带来了新的希望。
2013年,Google成立了一家全资的IT医疗子公司Calico,并且聘请了生物制药领域最有名望的领袖人物、基因泰克前CEO、苹果董事会主席阿瑟·李文森(Arthur Levinson)博士担任这家新公司的CEO。为什么互联网公司要进入医疗行业,为什么功成名就的李文森要到这家新公司创业呢?我们不妨听听李文森博士自己怎么讲。
李文森博士认为在过去的20年里,医学进步其实非常缓慢,只有IT技术结合生物制药技术,改善人类健康状况才有希望。李文森博士用他所熟悉的治疗癌症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讲,易然攻克癌症是人类的一个梦想,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种特效的抗癌药能够治愈癌症。过去医学界还试图研制这样的抗癌药,但是今天,医学界认识到,由于癌细胞本身的基因会变异,因此并不存在这样一种万能药。基于这一共识,医学界改变了治疗癌症的思路,那就是针对特定患者(不断变化的癌细胞),研制特定的药物,从理论上讲,只要研制的速度超过癌细胞变化的速度,癌症就可以治愈了。
按照传统的研究思路,科学家们应该先研究病理,找到解决方法(比如阻止具有某种基因的癌细胞蛋白质的合成),然后找到相应的药物,进行各种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这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强调因果关系的工作方法。但是,按照这个思路,为每一位癌症患者研制一种新药是很难办到的。目不说制药公司能否安排一个专门的团队为一个特定的患者服务,就算是能做到这一点,研制新药的成本也是患者无法负担的一一平均一个人要10亿美元。事实上,不仅研制抗癌药成本高周期长,在美国,任何一种有效的处方药研制都是如此。10年前,任何一种新药的研制就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10亿美元的成本。今天这个过程不仅没有缩短,而目还增加到了20年,而研制的成本也上升到20亿美元以上,今后时间和成本都还会增加。
针对这种困境,李文森等人想到了利用大数据来解决问题。他估计,采用大数据有望实现针对每一位癌症患者量身定制药物和治疗方法,而成本可以从每个人10亿美元降至人均5000美元左右。
大数据对医疗诊断的另一个主要的应用在于将人类的基因图谱和各种疾病联系起来,从而找到可能致病的基因,并目设法修复。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完成,那么不仅有希望治愈很多过去因为基因缺陷引起的绝症(比如癌症、帕金森综合症等),甚至有可能逆转人类的衰老过程。李文森博士介绍,采用传统的医学研究的方式,要想找到导致老年痴呆的基因并且找到治疗方法,在他有生之年(1950年出生)可能是看不到的,但是利用大数据,则有可能办到。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在六十多岁的高龄重新开始创业的原因,而Google仅第一期就为这个项目投入了10亿美元,此后还不断地投人巨资用于研究。可以想象,未来在这个领域获得成功的公司,必然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伟大公司。
在Google之外,人类长寿公司也在开展与Calico类似的研究。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是基因测序领域的先驱、著名科学家温特(Craig Venter)博士,他说服了一些医疗机构,特别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医学院将病人真实(未屏蔽个人信息)的医疗数据拿出来,研究基因和疾病之间的联系,以便帮助进行个性化制药。该公司有很多重量级的客户,包括著名的基因泰克公司。据基因泰克的科学家讲,目前的各种抗癌药其实只对有某些基因特点的人非常有效,而要研制出对其他基因特点的人有效的药品,就需要分析和处理上千倍的个人基因信息,这在过去成本高得无法承受,因此他们和人类长寿公司的工程师们合作,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学习,试图找到基因以及其他医疗数据和表征或者结果(Outcomes)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方面能够加快新药的研制速度,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根据患者特定的基因进行个性化制药。
在距离Google不远处,Google的前高级副总裁胡贝尔(Jeff Huber)所创建的圣杯公司装配了全世界最多的基因测序仪器(按照测序的能力计算,而非简单的数量),正在紧锣密鼓地研究癌症的早期检测问题。圣杯公司源于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仪器公司Illumina的一个内部项目一—通过检测人体血液中异常的基因,及早发现肿瘤。后来,在Google、盖茨、贝佐斯和乔布斯遗孀的共同支持下,该项目独立成圣杯公司,由胡贝尔担任CEO。圣杯公司检查癌症的方法是通过抽血进行基因检测,如果人体内出现了癌细胞,一些癌细胞的基因会体现在血液中,通过这种方法有望在癌症一出现时就发现。这种检测的成本比做全身高精度核磁共振(在中国目前是10万人民币以上)要低得多,Grail希望能够降到500美元以下(4000元人民币以下),这样就可以进行癌症普查,并且经常性地做检查。Grail可以通过验血给出四个结论:
是否有癌症;
如果有,长在了哪里?因为不同癌症的癌细胞基因不同;
如果有,发展的速度如何?一些癌症发展很慢,有些甚至会自愈,但是有些发展很快;
如果有,它对放射性是否敏感,对某种药物是否敏感?这样就知道应该如何治疗了。
这种方法还可以对癌症的发展情况、治疗情况进行监控,因此被认为是颠覆当今医学的革命。圣杯公司的核心技术,简单地讲就是大数据+机器智能+基因测序和分析。在美国,员工只有几百人的圣杯公司已经成为下一代医疗的标杆企业。世界上很多著名的医院、药厂都已经或将要开始与它合作。在圣杯公司第二轮融资中,以强生制药、默尔克、施贵宝等为代表的大药厂占了大部分,以高盛和拜尔斯(Brook Byers,凯鹏华盈KPCB中的B)为代表的投资银行和风险投资,以及以腾讯和香港陈氏兄弟为代表的亚洲资本,一同对它进行了投资。加上早期给它投资的Illumina、Google、盖茨和贝佐斯,可以说它得到了全世界半个IT行业、半个医疗和医药行业以及半个投资领域的背书。出于对圣杯公司创始团队的信任,以及对它技术的看好,更重要的是对这项事业的支持,我的基金也对它进行了投资。关于胡贝尔和圣杯公司更多的细节,大家可以参见拙作《态度》。
大数据医疗近年来非常热门,有很多公司拿这个概念炒作,但真正做事的比较少,能有所作为的就更少。很多IT企业其实并不具备成为大数据医疗公司的可能性。我们在前面说到,建立起基因、健康数据和(疾病)表征的对应是非常重要的,而这点大部分IT企业就做不到。找不到这种对应,即使发现一个人的某一段基因和其他人不一样,但对此会产生什么结果,大家并不知道。Calico公司的创始团队除了Google的IT工程师,主要是以李文森为首的基因泰克的科学家,他们是生物系统(Biosystem)方面的专家,但是即便如此,也只能把握IT医疗研究的大方向,很多具体的研究工作都给了大学、医院和其他公司。此外,Calico公司还与美国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以及杜克大学医学院在个人医疗数据方面展开了很深入的合作。即便有了这样的支持,李文森依然认为十年内未必能看到什么让人眼睛一亮的成就。类似地,圣杯公司易然得到了那么多明星企业和投资人的支持,也没有计划在短时间里盈利。
大数据和IT医疗行业市场足够大,需求足够强,一定会诞生未来的苹果和Google,但是这件事做起来难度也很大,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踏踏实实做事情的精神。
3.4 新绿色农业
农业(指广义上的)是人类最古老的产业。过去的几百年里,农业从来就被认为是每况愈下,在国民经济中越来越不重要的行业。很难想象农业和高科技会有什么联系。但是在历史上农业确确实实促成了一个重要的工业领域的诞生一一化工工业,并且这支撑着另一个领域一一生物技术。
从人类出现到约100年前的漫长岁月里,人类始终没有能很好地解决温饱问题。全世界绝大多数人被拴在土地上和庄园里,辛苦一年勉强生产出全世界够吃的食品。每逢风调雨顺,政治清明,温饱就暂时不成问题,否则就会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口处于饥馑的状态。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有4条:缺乏机械,缺乏水电,缺乏肥料和农药,缺乏良种。100多年来,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这4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西方工业直到二战前,基本上以机械工业为主导,在19世纪末农机开始在西方国家倬用,并在20世纪初得到普及。有了机械和化石能源(石油、煤和天然气),世界上的农田基本建设在短短几十年间基本完成,基本上做到了旱涝保收。而20世纪初,化工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造就了道尔化学、杜邦化学公司这样当时的高科技公司。从社会影响力来看,当年的杜邦公司可一点不比今天的微软和苹果差。这些公司将农业转变为生产粮食的“工业”,以致一个农业工人就能完成过去十几个人的劳动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对基因的了解和生物科技的发展,人类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培养出的“良种”超过了20世纪以前人类历史上的总和,解决了农业的单产问题,释放出大量的耕地提供给城市化发展。到20世纪末,全世界除了有战乱和独裁统治的地方,没有人们吃不饱的国家。
凡事都有好坏两方面,随着工业化向农业渗透,以及生物技术,主要是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中的推广,一方面农业的收成成倍增加,而成本又降得非常低,倬得全世界总体上由“不够吃”变成了“吃不完”。在西方的主要农业国,是在为生产的东西太多没人要而发愁,在法国甚至出现葡萄酒比矿泉水便宜的怪事。另一方面,全世界的人却“越吃越不健康”,除了农药和化肥等带来的污染,还有转基因食品对人身体带来的潜在威胁(这一点至今很难有结论)。因此,当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个人收人有了大幅提高后,人们又开始从“吃得饱”转而追求“吃得健康”。
但是我们每人每年花在农产品上的钱并不少,或者说这个产业并不小。在农业上的一点突破,比如中国的杂交水稻,很容易拓展开,它的效益比Google不知道大多少。实际上,如果有一种商业模式让当年的袁隆平教授垄断了杂交水稻技术,他的公司也许会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但是,农业的研究和制药业一样,周期很长。如有能在近几年内见效的技术,一定是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研究的。很遗憾,我不是农业专家,也没有跟踪过农业技术,不知道世界上哪些农业技术会像化肥或杂交水稻那样带来革命。但是,我相信一定存在这种技术,不远的将来就可能出现。这一次,它能让我们从“吃得饱”到“吃得健康”。而目,随着全社会对食品安全的担心,投资领域对“吃得健康”的项目会逐渐增加投人,最终会倬这个行业产生质变,机会也就在其中。
3.5 电子商务
下面这一段内容是我3年前在本书第三版中写的,只字未改:
电子商务的历史比Google更长。可能有些读者会怀疑这个互联网上“古老”的行业是否还会有新的机会。但是,电子商务成长缓慢,实际上才刚刚起步,可以用“方兴未艾”来形容。过去15年,电子商务在美国零售业中占的比例呈直线上升,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2008—2009年也是如此,这个趋势至今没有减弱的迹象。到2015年第二季度,电子商务在美国零售中占7.4%,每年金额达到5500亿美元左右,成长空间还非常大。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虽稍稍滞后于美国,但是增长速度快。在2009年时中国的电子商务还只占到零售的2%左右,绝对交易金额相当于美国2000年的水平,但是到了2011年底,中国电子商务已经占到零售的4.3%,交易金额达到1200多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005—2006年的水平,发展速度远远超出预期。到了2015年的上半年,电子商务占到零售市场的11.4%,折算到全年,相当于每年3.2万亿元人民币,和美国相当。全球电子商务依然在蓬勃发展,市场空间巨大,足以容纳一两个新的Google。但是在美国电子商务已经走向成熟,这方面的大机会其实已经不存在了,原因有二。
首先,eBay和亚马逊的两种商业模式都是成功的(详见前面介绍商业模式的一章),虽然它们各有千秋。在中国,人们喜欢使用商家对商家(B2B)、商家对个人(B2C)和个人对个人(C2C)的说法。套用这种说法,eBay的模式基本上是B2C和C2C的结合,而亚马逊基本上是B2C。在美国,商业的门槛非常低,个人和商家没有本质区别,人们更喜欢把它们按照分散和集中的管理办法来区分。事实证明,只要电子商务中的欺诈行为存在一天,亚马逊的集中管理就比eBay的分散式管理更能让消费者放心。由于亚马逊和eBay的存在,美国电子商务本身已经无法创造出Google那么大的新公司了。
众多的电子商务小商家,实际上要依靠Google,或亚马逊和eBay存活,因为这三家是小商家网络访问流量的来源,它们的发展只会强化这三家公司的地位,就如同以客户端为核心的个人计算机软硬件的发展只能强化微软和英特尔的地位一样。
第二个原因是,在美国,像沃尔玛和家得宝这样的连锁店系统非常发达,几乎渗入到每一个社区,人们可以很方便地买到便宜的日常用品。何况这些连锁店也逐渐将生意扩展到了互联网上。
而在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电子商务的潜力却可能造就出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型新型公司。这里面有很多美国不具备的条件。第一,由于这些国家电子商务占GDP的比例比美国低很多,成长的空间大得多。第二,电子商务的产业链很多环节都不健全,比如支付和物流,这便有了更大的机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美国在没有电子商务时,已经铺设了全国乃至全球的零售网。在美国,主要的零售店都是连锁的,几乎无所不在,无论你住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很方便地到附近的沃尔玛等连锁店买到所需的商品。在中国,零售网还未建立起来,电子商务便出现了,因此中国可能会跳过铺设全国零售网这个过程(毕竟在全国开1000家超市不仅成本高而且周期长),代之以电子商务。中国可能永远不会出现沃尔玛,但是会出现一个和沃尔玛一样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事实上,中国的京东商城就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在这一节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在中国的电子商务领域要防止泡沫,因为没有根基的泡沫不可能造就一个千亿美元的公司。2011年可以说是中国电子商务的泡沫年,由于团购的效应,砸到电子商务(包括团购)中的风投资金不计其数,但是没有产生一个像阿里巴巴那样像样的公司。而世界上最早做团购的Groupon公司,增长已经迅速放缓。中国一些电子商务公司上市后因为业绩不佳而股票大幅缩水,而未上市的公司长期亏损,依然看不到盈利的希望。目前在中国,整个电商领域盈利较好的只有阿里巴巴一家,外加个别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的小公司,其他公司要么是靠继续烧投资人的钱,要么找不到后续投资而关门大吉。就连目前炙手可热的京东商城,虽已上市,市值也不低,但是距离盈利还要走很长的路。相比之下,美国电子商务烧掉的风险投资要比中国少很多,目前这类公司大多数盈利情况良好,在这些方面,美国的很多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如今,三年过去了,三年前我对电子商务未来的判断完全得到了印证。
- 首先,中国电子商务在快速发展,而目总量很快超过了美国;
- 其次,美国没有诞生新的大型电子商务公司;
- 最后,易然2016年大家都觉得中国的电子商务格局已定,就是阿里巴巴和京东竞争,谁知还杀出了一个拼多多。今天拼多多的市值已经和京东相当了,这就是我所说的电子商务的机会所在。
倒不是我预测得准,而是因为一个产业发展的浪潮一旦启动,就会顺势而为很长时间,电子商务便是如此。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站在浪潮之巅顺水推舟,要远比没有目标拼命划船合算得多。
3.6 移动互联网和IoT(万物互联)
下面的内容是我在本书第三版中所写的,也是一字未改:
随着高速移动通信技术(3G和4G)的普及,苹果和Google这两家最有活力的技术公司进入无线通信市场,无线业务将迎来一场全面的革命。历史上,历次技术革命都会缔造出新的王者,这次也不会例外。
到目前为止,智能手机的格局完完全全重复了30多年前PC革命的模式。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它,我们不妨简要回顾一下30多年前PC产业的格局。
苹果公司首先发明了个人电脑(大学没毕业的史蒂夫·乔布斯也因为“开创和发展个人电脑工业”入选美国工程院院士),并且最早推出了非常艺术的、具有图形界面的麦金托什计算机。在商业上,苹果是通吃从芯片(和摩托罗拉合作)和硬件设计,到操作系统,再到应用软件整个PC生态链的各个环节,尤其是软件价值通过硬件实现这个商业模式。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当然,坏处也非常明显,就是成本高、价格高,于是苹果的产品成为有钱人而不是大众的产品。因此,它的市场份额在经过了开始的领先期后,就稳定在一个5%左右的细分市场上。
而当时,另一种更成功的商业模式是所谓的WinTel体系,即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加上英特尔的处理器,其他所有PC的软硬件厂商向Windows和Intel靠拢。这个模式创造出庞大的PC产业,包括巨大的销售额和大量的从业人员。但是在这个产业中,真正长期稳定挣到大钱的公司只有“2+2”一共4家。除了分别垄断操作系统和CPU芯片的微软和英特尔两家外,还有在众多PC厂商中经过生死搏斗打拼出来的两家最大的PC厂商惠普和戴尔。前者代表了老一代计算机公司转型到以PC为核心的公司成功的案例,而后者代表了赶上PC时代的新贵。其余的公司,有些抓住时机红火一阵挣了点小钱,有些连这点小钱都没有挣到,还有一些时亏时盈,勉强维持局面而已。而这些被淘汰的公司中,不乏曾经大名鼎鼎者,比如网景、莲花、康柏、DEC、WordPerfect、Informix、Sybase、Gateway,等等。
现在,苹果还是当年的苹果,走的依然是当年的老路,它从头吃到尾。这样,它无法依靠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力量将自己的产品做成主流产品。这和乔布斯及苹果的基因是分不开的。因此,虽然苹果在一开始可以靠领先的产品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但是当大量低端用户开始使用智能手机后,苹果的市场份额会下跌,它最终还是只能占到智能手机市场5%左右的份额。而在智能手机方面,类似WinTel的格局已经形成。Google的Android取代了当年微软Windows的地位。在第一版中,我们是这样描述Android的前景的:
虽然它现在只占智能手机市场的1/10不到,但是前进的势头是包括苹果在内的任何公司都无法阻挡的。
2012年安卓智能机果然占到了智能手机市场一半以上的份额。苹果公司再厉害,也斗不过有几十家跨国公司和运营商组成的安卓联盟。到了2015年,安卓占了全球智能手机操作系统近九成的市场份额。而在处理器方面,早期有高通和三星为首的两大三小(华为的海思、美满Marvell和博通)五家半导体公司,后来美满和博通基本退出了市场,中国的紫光(收购了展讯)加入了进来,这些公司用的都是英国ARM公司的设计因此几家ARM系列公司像当年像英特尔和AMD那样控制处理器芯片的格局已经形成。抛开操作系统和处理器,现在做一款智能手机就像当年攒一台PC一样容易,谁都能办到。而正是因为谁都能办到,所以在手机制造上挣钱是很难的事。当然手机制造还需要有惠普和戴尔这样的角色。在传统的手机生产商中,起步较晚、市场份额较低的三星公司,很快放弃了传统手机的业务,专注于安卓的智能手机,取得跳跃式发展,超过了摩托罗拉、诺基亚和苹果等公司,成为出货量最大的智能手机厂商。我本以为较早进入这个市场的摩托罗拉能够在安卓时代重现当年惠普公司一举拿下PC市场份额第一的奇迹,但是事实证明这次是一个亚洲公司——三星。在第一版完稿时,戴尔这个角色在手机领域尚未出现,虽然我们知道它应该是一个带有全新理念的新公司。我当时分析,“如果完全按照传统PC产业来分析,这是剩下的唯一出现Google这种公司的机会。”现在看来,中国的小米科技公司很有点像当年的戴尔,它按照运营互联网的思维方式做手机业务。虽然它还是一个很小的创投公司,但是在2013年小米智能手机出货量已经上千万部,这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智能手机市场都占了不算太小的份额。而这从无到有的过程也仅仅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到了2015年第三季度,小米手机的出货量已经达到了1800万部,更重要的是,它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还远没有排到第一位时,就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这显示出中国新一代科技公司在国际化方面比阿里巴巴或者腾讯等上一代公司做得更好。到2014年底小米科技的估值高达450亿美元。和小米科技在手机量上不相上下的联想,整个集团公司的市值也不过110亿美元众所周知,手机只是联想业务的一部分,还不是最赚钱的部分,为什么产品只有联想一个子集的小米能获得如此高的估值呢?著名投资人、DST风险投资公司的创始人米尔纳(Yuri Milner)认为,小米不是像传统硬件厂商那样单纯靠销售硬件微薄的利润挣钱,而是通过互联网的新模式获取了硬件用户。今后,它很容易将各种其他硬件产品,比如电视机和平板电脑推销给它的互联网用户。米尔纳认为小米有希望成长为一家千亿美元的公司。如果三星最终成为手机时代的惠普,而小米能成为这个时代的戴尔,那么亚洲就将在这个时代的IT领域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本章第四节还会专门介绍亚洲的机会。
但是,话又说回来,智能手机这个市场虽然巨大,但是如果重复PC产业的老路,产生一个新的Google的机会并不多。最多能有一家新的戴尔,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戴尔。
好在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在智能手机时代,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服务会比PC时代带来更大的商机。Google公司就是基于这一点考虑,才敢于免费开放它的安卓操作系统。但是,移动互联网的增值服务远不是Google一家能吃下的。虽然目前在手机上最容易挣钱的应用还是搜索,而且手机搜索的商业转换率甚至好于传统互联网上的搜索,但是,从长远看,基于手机的支付和社区(包括游戏)的商业前景非常乐观,毕竟Google在这两个领域并不很领先。
让我们先看看手机社区。在第一版中我预测短信市场会消失,替代产品会出现,当时我的看法如下:
短信曾经是亚洲手机市场的一个支柱,在中国更是一度占据了手机市场的半壁江山(这要感谢中国通信运营商高话费的商业政策,使得人们把移动电话中的电话功能降级到次要位置,取而代之的是较为便宜的短信)。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预测,随着手机社区的出现,短信这个业务有可能在中国和亚洲迅速萎缩,就如同Facebook出现后,它的用户写电子邮件的数量大幅减少一样。那么这部分市场有多大?可以说,当初的短信市场有多大它就有多大。在中国,短信创造出一个腾讯。那么手机社区至少还应该能创造出一个这么大的公司。
2012年,在本书的第二版中,曾经有上亿用户的手机QQ基本上已经没有市场了,对于当时刚刚出现的米聊和微信产品,我是这样评价的:
事实上2010年底,小米科技公司推出了一款叫做“米聊”的智能手机通讯工具,支持多个手机平台,不限移动运营商,它通过Wi-Fi或者移动互联网,实现文字短信、语音对讲、图片和多媒体的传输等功能,同时具有社交网络和通讯双重功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当然,腾讯公司后来居上推出了类似产品微信最终垄断了这个市场。虽然米聊和微信还只是利用移动互联网特点在通信和社交网络上比较初级的尝试,但是向用户展示了移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在社交网络上的便利性和潜在的价值。
两年后我的预言再次得到证实。基于手机的社交得到了充分的发展,WhatsApp、腾讯的微信和Snapchat等都通过手机建立起巨大的用户群。到目前为止被Facebook以190亿美元收购的WhatsApp和腾讯的微信做得最好。遗憾的是,它们都不是独立的公司,也就失去了单独进入千亿美元俱乐部的可能性。在2014年Facebook高价收购WhatsApp时,很多人质疑这样高的价格是否合理,不过对比微信的价值就能发现其实Facebook买得还是很划算的。在腾讯1800亿美元左右的市值中,微信提供了超过一半的价值,没有微信,腾讯的价值连一半都到不了。这样算下来,微信本身值900亿美元左右,而Facebook收购比微信用户数更多的WhatsApp只花了不到200亿美元,还是很划算的。
在手机社交领域,目前最大的独立运营的公司要算青少年分享图片的Snapchat了,但是它的用户群过于年轻化,产品变现也比较困难,成为千亿美元公司的可能性很小。
我在2012年的本书第二版中还预测——
如果再往前看几年,最终能够取代Facebook的公司,应该是在移动互联网社区上——它会把以前互联网上的虚拟社区和现实生活的圈子有机地结合起来。
今天大量O2O公司的出现证明了用户在线上的活动可以和线下的生活结合起来,但是要做出千亿美元的公司,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从目前发展的速度看,或许在线房屋租赁平台Airbnb有这个可能,2015年7月它的估值已达250亿美元。
手机支付也将是一个了不起的行业。这里讲的支付不是过去那种给个手机号,发个短信的支付,而是利用智能手机的加密蓝牙和身份验证功能,取代信用卡在任何零售商店完成支付交易。电子支付无非是要确认个人身份。手机是个人身份最好的验证手段,它具有便携、通信方便的好处,并且可以根据安全需求加入多重保护,包括密码和生物特征(指纹、面孔和虹膜)。在商店里,手机支付可以简单到把手机往收银机上一放就能完成转账。
相比信用卡支付,手机支付更方便的地方在于,它可以进行个人之间的交易。信用卡支付需要一个接收信用卡的机器,这只有商家才有。而手机支付可以简单到只要两部具有蓝牙功能的手机即可。只要输入和确认交易的金额,两部手机互相一“碰”,交易就完成了。当然,出门坐地铁和打车也是同样简单,只要在地铁入口“碰”一下,或者在出租车司机的手机上“碰”一下即可。做到这一点,我们今后就不需要带什么现金了。这里面的难点不在手机上,实际上今天的智能手机已经能提供这项功能了,手机支付的关键在于建立起相应的商业网络和结算系统。
2012年夏天,星巴克公司宣布了一条消息,它今后的信用卡和记帐卡的交易将通过一家叫“Square”的小公司提供的电子支付服务进行,同时给这家小公司注资2500万美元。这家小公司给商家提供一个水果糖大小的装置,可以和付款者的手机相连进行付款。这样装有它App的手机就成了信用卡,同时这些手机之间可以互相付款结算。这家小公司成立于2009年,但是发展迅速,短短三年后,2012年它的估值已经到了10亿美元。又过了三年,Square作为第一家独立的移动支付公司上市了,到2015年底,这家依然亏损的公司市值已达40亿美元。虽然我们还不能断定它今后就是这个行业的老大,何况40亿美元的市值离我们千亿美元的门槛相去甚远,但是这个行业最终的老大一定会是一家有影响的跨国公司。
今天,几年又过去了,移动互联网产业格局的变化基本上如同我在几年前所说的那样。当然,我在几年前留下了一些未填上的空缺,今天已经有企业给补上了。比如谈到移动支付时,当时还看不到哪家企业会做得最好,今天从交易笔数上看,是腾讯的微信支付做得最好。我还讲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定会有类似戴尔的公司诞生,今天来看它就是小米。但是,在PC时代从小型机转型到PC成功的企业还有惠普,这个我没有提到,今天中国的华为和vivo/OPPO都颇具当年惠普的风采。这些都说明,尽管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科技产业的发展是有章可循的。
当今的移动互联网应当算是第二代互联网,第一代是基于PC的,接下来的万物互联则是第三代互联网。我在“得到”的专栏《科技史纲60讲》以及新出版的《全球科技通史》一书中介绍了它的发展前景,这里就不赘述了。在万物互联这个领域,必将诞生新一代的Google。今天全世界的电信产业(包括运营商和制造商)比互联网产业大一个数量级,一年的营业额高达4万亿美元。IoT(以及今天媒体上常说的5G)时代到来后,按照最保守的估计,这个市场也会翻一番,这足够容纳不止一家千亿美元的公司。至于在IoT时代最重要的技术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新一代的处理器和操作系统。这就如同在WinTel时代是微软的Windows和英特尔(Intel)的处理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是Google的安卓操作系统以及ARM的处理器一样。
3.7 线上到线下(O2O)的结合
线上到线下(Online 2 Offline),即中国现在经常说的O2O,也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领域。我在本书的第三版中只是写了下面短短的一段话:
我们在前面多次讲到,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与人的联网,一定会带动原来看似和互联网关系不大的行业的彻底变革。从2008年起,一些O2O的公司在世界上兴起,并且做得风生水起。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在网上租赁房屋的Airbnb公司、打车公司Uber以及中国同类的公司滴滴出行。这些公司代表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前景非常光明。关于O2O本身,我在另一本书《见识》中已经有很多描述,这里我们就不重复相应的内容了。不过有一点值得强调,那就是在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连接比拥有更重要。Airbnb不拥有任何一间房屋,它只是连接房东和租户的桥梁,但是它的生意比世界上任何酒店集团都大。类似地,Uber和滴滴出行几乎未拥有任何出租车,但是因为它连接了司机和乘客,客流量超过任何一家出租车公司。通过互联网共享资源是未来社会的特点。
对于O2O,在过去的一年里它显然没有之前热门了,有人可能会说“你预测错了,高估了它,它就是泡沫”。其实,绝大多数O2O企业死掉了,并非证明这件事本身不靠谱,而恰恰标志着中国的O2O在走向成熟。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多次说到,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会产生很大的泡沫,绝大多数企业都会死掉,但是如果留存下一些好的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企业,则说明它是技术革命,而不是单纯炒作概念的泡沫,中国的O2O也是如此。今天中国人或多或少地在生活中享受到了O2O的好处,从美团外卖到滴滴打车都是如此。这两家公司也成为了市值(估值)上百亿美元的大企业,可以说是从本书上一版(2016年)至今发展起来的下一个Google的候选企业。
3.8 新的汽车产业
这一点本书“汽车革命”一章已有详细介绍,就不再赘述了。总结一下,新型汽车产业足够大,足够诞生千亿美元级的公司,特斯拉无疑是最佳的候选。不过,正如我们在27章中所讲到的,在电动汽车时代,中国有望出现全球性的汽车公司,就如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出现全球性的手机公司一样。
3.9 人工智能
自从2016年Google的AlphaGo战胜李世石,人工智能无论是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还是在工业界,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关于这一点,我在《智能时代》一书中已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在这个领域诞生一家千亿美元级别的公司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智能革命,而在历次重大技术革命过程中都诞生出了伟大的公司。
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不可能产生新的伟大公司,这主要是因为在美国引领这项技术发展的是Google、微软和IBM这些大公司。但是在中国,诞生新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公司则有可能。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目前大的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水平,和Google、微软、亚马逊等公司相差一个数量级,易然一些媒体把中国的这些企业和美国的对标企业一同报道,但是它们在技术上不在同等水平,这就如同说中国的恒大、上港是(中国的)足球冠军,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也是(西班牙和欧洲)足球冠军一样。两类冠军水平相差甚远。没有了现有企业的压制,新的企业就容易发展起来。其二,中国目前的商业环境比美国好,中国是全国上下一致要通过智能产业完成国内工业的升级换代,而美国左派技术精英在非法移民问题上操的心比在利用人工智能上更多,企业界很多人士则显示出虚伪行为,他们一方面积极拥抱新技术,一方面宣称美国的工业已经完蛋了,要想继续在技术上领先就需要到海外而不是留在美国发展。因此,美国的企业界在行动上并没有打算在美国本土大力发展人工智能。至于美国民众,大部分除了关注平等和平权问题,对新技术普遍漠不关心。在2016年AlphaGo和李世石对弈时,很多美国人都在睡大觉,或者在酒吧喝酒,观看实况转播的人不到百万,而在与这件事无关的中国,有2.8亿人口(几乎相当于美国的人口)在看实况转播。从这件事就能看出两个国家对人工智能态度上的差异。
4 关注中国
……
当然,中国新一代公司和伟大的公司还有很大的距离。那么,怎样才能培育出更多伟大的公司呢?这需要在法律和商业道德、国际化和创新性上得到根本的提升。法律上的问题这里就不多讲了,实际上缺少对版权的保护,毁掉了整个中国的软件业。由于没有对奸商处以重刑的惩罚制度,中国至今很难有高质量的世界品牌。国际化的重要性不难理解,一家跨国公司肯定不能只为一个国家服务,而中国大部分优秀公司依然没有像盛田昭夫或者本田宗一郎那样能走出国门,将企业和产品推向全世界的领军人物。而在创新方面,亚太国家,尤其是中国,相比美国有明显的不足。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至今主要靠勤劳而年轻的劳动大军,而不是靠创新力。而过去以仿制出名的日本,现在在创新上已经是世界一流。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日本人发明了高铁、卡式录音机和录音带、商业的五寸激光唱片(CD)、游戏机、蓝光DVD、混合动力汽车等。进入21世纪后,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中,日本以18年18人获奖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中国目前IT领域的最大问题有两个。第一,几乎找不到有一万小时工作经验的工程师,因为一个年轻人毕业五六年后就开始从事管理工作,以至于一线研发的工程师永远是欠缺经验的。所以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总是给人“便宜但低质”的印象,很难占领产业链的上游。第二,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很快,市场很大,IT公司不需要把产品和服务做得很精,就能获得市场并快速增长,很多成功靠的是运气而非实力和水平。这些公司的领导人,在公司收入从一个亿增长到100亿时,能力显然没有增加一百倍,但是“谱”却随着收人的增加而增加。一旦到海外和跨国公司竞争,就时常碰壁了。真正成功的跨国公司在人员构成上,尤其是高层人士的构成上都是国际化的,多元文化的撞击不仅能创造出伟大的产品,而目会成为全球竞争力的保障。相比美国的大公司,中国优秀的公司在人员构成上还过于单一,要想彻底做到多元化,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虽然很多人可能要挑战我的上述观点,觉得它们有些迂腐,觉得利用资本的力量和借鉴一些技术弯道超车会来得更快,不过很遗憾这就是事实。中国在四大发明之后,除了杂交水稻以及量子通信,对全球科学和技术革命性的贡献几乎为零。100多年前,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时候,依靠的不是任何资本泡沫,而是爱迪生和西屋(发明电和交流供电)、贝尔(发明电话)、福特(发明T型汽车)、怀特兄弟(发明飞机)等这样一大批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发明家,以及洛克菲勒(石油)、卡内基(钢铁)、杜邦(化工)等搞实业的工业巨子。当然,爱迪生、西屋、贝尔和福特等人也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实业家。他们从事的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科技的进步,不可能通过房地产泡沫或者股市泡沫来实现。
中国的现实问题是,人们似乎不需要靠科技的进步和实业就可以取得财富。看看中国富豪榜的构成,有几个是贝尔、福特这样的发明家,又有几个是洛克菲勒和卡内基这样的实业家。几乎所有富豪的财富,或者来自于股市,或者来自于房市。当人们不再把房市、股市作为最快的挣钱手段时,不再玩一轮轮融资吹泡泡的游戏时,就是中国可以诞生下一个Google的时候了。
从经济的发展来看,中国诞生许多世界品牌和跨国公司是历史的必然,这个任务将落到年轻人身上。但是,目前最大的障碍是全中国非常缺乏各种顶级的技术人员,因为几乎所有的年轻人做不了几年技术就去做管理了。这种社会风气不是短期可以扭转的。最快的解决方法就是从世界各地引进顶级技术和管理人才。有了人才,有了经济的发展,中国才有可能诞生下一个Google。
结束语
科技产业最让人振奋的是,有新一代技术的革命的同时伴随着新一代公司的诞生,这个时间可能会很长,但终究会到来。而代表新技术的公司有时是新生的,有时却是以前的公司进化而来的,不论是哪一种都足以振奋人心。寻找下一个这样的机会,永远是现代社会中所有活跃的人追求或谈论的主题。
后记
很多人读了《浪潮之巅》后都问我:“作为一个计算机科学家,你为什么写了这么多书,而目涉猎如此广泛?”甚至有人以为我曾经是Google研究经济的科学家。
这本来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教育原本就是应该培养具有多种特长的人才,而不仅仅是一个很窄的领域的专家,这一点我在拙作《大学之路》中反复强调了。但是,由于国内的教育实际上走的是专才教育的道路,能撰写论文之外其他专题书的人很少,大家才会有此疑问。
其实,大部分科学家并非如同宣传的那样,是戴着厚厚的眼镜,言语木纳,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在真实的世界里,很多科学家,比如在《浪潮之巅》中提到的斯坦福大学前校长亨尼西院士,Google董事会主席施密特(美国工程院院士),太阳公司的创始人贝托谢姆,DSL之父西奥菲院士,WebEx的创始人朱敏,以及大家熟悉的李开复,这些科学家在商业上都非常敏锐(Business Savvy),而目取得过成功。另外,有一些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在学科之外的领域也是出类拔萃的,比如图灵博士是世界级的长跑好手,曾经战胜过奥运会亚军,索尼公司前总裁大贺典雄既是一流的工程师,也是专业音乐人士,他定义了我们今天激光唱盘的格式。在中国提倡大众创业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通才,特别是企业家们需要了解技术,工程师们需要具备商业头脑。
当然,人的商业知识和眼光不是天生的,需要不断地、用心地学习。Google早期的时候,创始人拉里·佩奇经常是一边和我们一起吃晚饭,一边研究着某个公司的财务报告,一边分享他的体会。Google最早的许多员工同样对商业很感兴趣。当然,要系统了解商业,就需要有专业的老师。因此,我要感谢自己身边的很多专业人士,包括投资银行的基金经理,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家,跨国科技公司的执行官,以及很多成功企业的创始人,这些朋友都是我的老师。我用心去了解商业的规律,本意是为了投资;不仅仅是为了让我管理的基金投资有好的回报,更重要的是让我一生的时间投资有效。对我而言,时间才是最大的财富,我要把它投到最有意义、最有影响的地方去。经过我的学习、思考和实践,我认定这样一个规律:科技的发展不是均匀的,而是以浪潮的形式出现。对个人来说,看清楚浪潮,赶上浪潮,便不枉此生。
读者们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写《浪潮之巅》?”
我的初衷是为了让中国的读者了解美国,了解科技产业,而不是写一部IT史记。正如大部分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一样,很多中国人也不了解美国。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很多来自于好莱坞的电影、麦当劳、名牌时装和化妆品;2008年以后还包括了金融危机、债务、霸权,以及这两年的贸易战等很多负面因素。这些东西固然是美国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也仅仅是一部分。科技公司、创新力及商业的公平性也是美国的一面,而目是更重要的一面。正巧2007年,Google中国黑板报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版面,让我有机会向中国的读者介绍世界级的科技公司及它们的成长规律。
科技工业和传统工业不同,它的发展很快,能够赶上并抓住机会的是少数人,我们早年倬用的很多科技产品,包括卡式录音机、录像机、胶卷照相机、针式打印机、计算机软盘、阴极射线管(CRT)显示器的电视机和显示器,现在已经消失了,而我们的子孙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找到它们。当然,和它们相关的技术也就不再需要了,这让很多风光一时的公司落伍,很多专家被淘汰。中国有句古话“女怕嫁错郎,男怕人错行”,的确如此。我写这些内容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帮助更多的人看清科技工业的发展规律,抓住机遇。
科技工业的快速变化,倬得我需要不断更新这本书的内容。而每次更新内容,又督促我认真地了解产业发展,学习新知识并总结各公司的经验,因此,写作和修订这本书也成为了我学习的过程。从2014年底开始,我辞去了Google的职务,专职做投资,主要目的就是便于把握IT行业的变化。今天,《浪潮之巅》已经出到第四版了,如果算上最初的黑板报,这应该是第五版了。在这一版的一些章节里,我有选择地保留了前面几版的内容,以便读者对照,看到科技工业的变化,也看到我思考问题的方法。
读者们经常问我的第三个问题是,“你的写作是跟谁学的,因为很多学文科的人,写出来的东西也不如你生动?”
谈到写作,我在这里要感谢两个人。第一个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余顺吾先生,他曾经是一位编辑。几乎所有的中学生,为了文章写得漂亮,常常苦思冥想编造动人的情节,寻找华丽的辞藻。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的这位语文老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彻底改变了我写作的方法。他让我关注内容,用朴实的文风表达自己的体会。第二个人是我在美国的导师库坦普(Sanjeev Khudanpur)教授,他训练了我说话和写作的逻辑性,比如怎么立论,并用论据支持论点。他是一位细节大师,要求我做到在公众场合讲话时,不多说哪怕是一句废话,也不落掉任何一句关键的话。其实,要想写得好,首先要说得清楚。然后,再用大家喜欢的语言,把要说的话描述出来,就形成了好的作品。
第四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美国是否没落了,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个人的看法是美国依然会很强大,易然它可能没有半个世纪前强大。从以下表中所列的改变世界的发明,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有科技竞争力的国家。其实即倬在经济上,美国的问题也远没有大多数中国人想象的那么严重(比如,美元的发行量其实比人民币少很多,这个我会在今后的博客或书中说到)。中国成为G2中另一极的希望很大,能不能成功,关键要看能否像日本那样有真正开放的心态,积极吸收世界各国文明的精髓。要想超越美国,路还很长,大家要有信心和耐心。中国的优势在于,时间在中国这一边,而需要警惕的是,因过于急于求成而将一手好牌打烂。
希望在一个世纪之后,后人再次填写这样一张表格时,在“国家”这一栏里大部分填的是中国。
2019年4月于硅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