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前言
很久很久之前就打算读完这本书,但一直拖到了现在才读完。由于是台湾出版的版本,应该没有删减。
这本书让我手里着实多了不少「武器弹药」。虽然我早就知道内容了~乐~
书中的知识分子大多人际关系尤其是家庭关系恶劣,滥交,极端自私,嘴上热爱全人类,实际上最多爱自己,多一个都不行。
本书作者保罗・约翰逊也能看出卢梭和马克思思想中的「宗教」色彩,但显然没能更进一步地分析背后的「亚伯兰罕一神教」。当然,地球上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看到这点。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中国反动派,毕竟很难找到比儒教更加反动的群体了。
下面的正文摘录主要集中于卢梭和马克思两大教主,这两个人物也是书中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两个知识分子。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一个人的德行确实很能体现一个人的「德行」。
人的精神始终应该立足于宗族乡党,外扩为天下国家,这样才不会沦为「热爱全人类却不爱自己孩子」的「人类之友」。
天下加上化外之地才等于世界。虚幻的全人类就让精神错乱的「渣滓」去热爱吧!
每个人应该先爱他自己 ——— 然后才是家庭 —— 祖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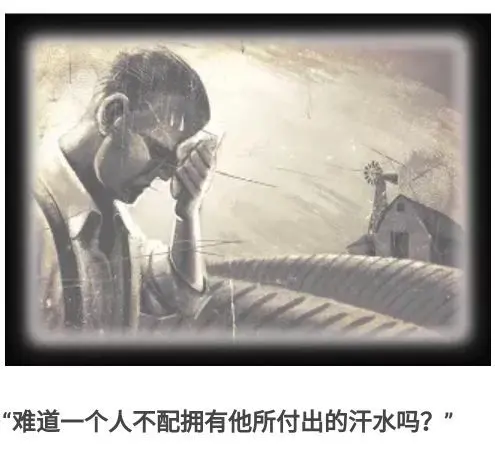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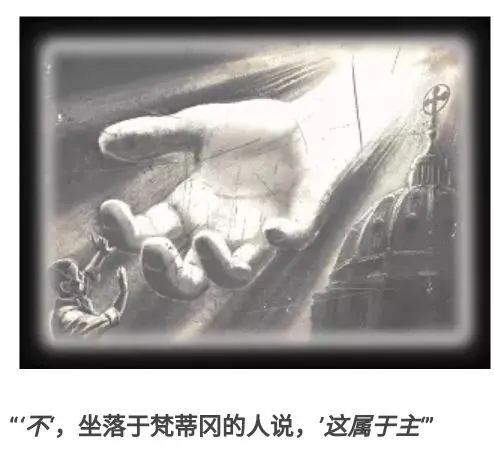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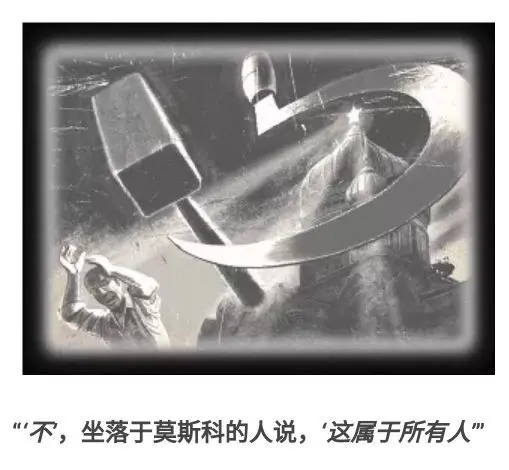
【注:不不不,这属于我。】
至于虚无缥缈的全人类,全灵长类,全哺乳动物,全脊椎动物 ————— 让脑子出毛病以至于精神错乱的左派分子去爱吧!

把知识分子和士相提并论和把亚威(耶和华)当成上帝一样令人发笑!不管大陆还是台湾,都成沦陷区了,沦陷区大部分人的膝盖骨早就跪没了,卑微到了尘埃里!
书籍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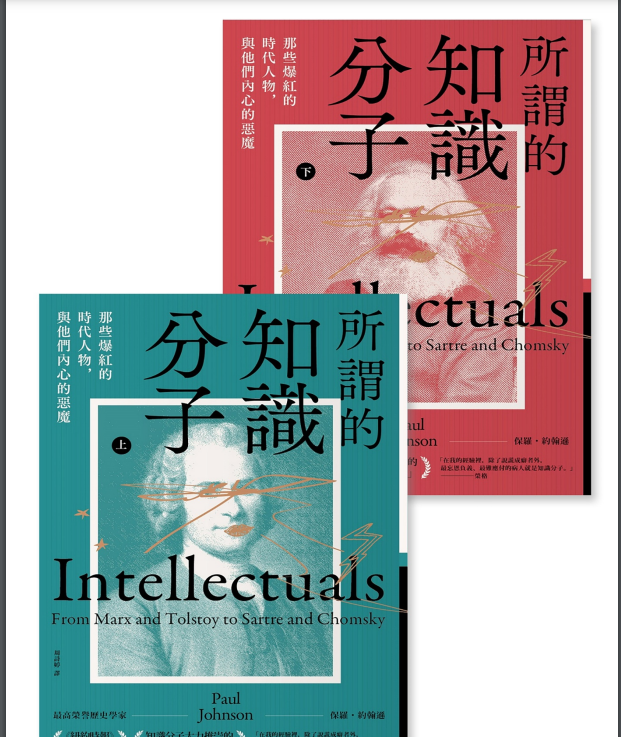
作者:保羅.約翰遜
出版社:一起來出版
副标题:那些爆紅的時代人物,與他們內心的惡魔(上、下冊不分售)
原作名: Intellectuals
译者:周詩婷
出版年: 2021-5
ISBN: 9789869911580
作者简介
保罗・约翰逊 (1928 一 2023)。约翰逊毕业于牛津大学麦格德林学院,此后一直担任《新政治家》的编辑 (至少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他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著作极丰,有 20 余种,大都是政治和历史作品,诸如《犹太人史》、《当代》(此书江苏人民出版杜将在 2000 年出版)、《英国人民史》等,其中最著名、争议也最多的就是他的《知识分子》一书。
内容简介
1998 年,《知识分子》在伦敦出版,立即引起大西洋两岸的强烈反响,在英国和美国一版再版,始终畅销不衰。首版后立刻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
本书中谈论的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埃德蒙・威尔逊、维克多・高兰茨、莉莲・赫尔曼等人,有些是我们耳熟能详又深深敬仰的思想家和作家,有些还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如今,作者为我们更全面地解析这些思想大家的日常生活。他们在生活中是如何管理自己的?如何对待与家人、朋友和同伴的关系?如何处理性和金钱的问题?《伦敦书评》曾发表文章称本书是 “一本有说服力的、也是有趣的书;即使不喜欢它的人,也会从中得到乐趣”。
本书拉近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距离,带给人们对人性更多的理解。
正文摘录
第一章 盧梭:沒有朋友的「人類之友」
Jean-Jacques Roussrau 1712-1778
「他的醜陋足以嚇壞我,而愛情並未讓他增添風采。但他是個可憐的傢伙,我用仁慈與 溫柔待他。他是個有趣的瘋子。」 ── 烏德托公爵夫人,盧梭的情婦
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在過去兩百年來穩定增長。更確切地說,從歷史的長期觀點來看,世俗的(相對於宗教的)知識分子成為形塑現代社會的關鍵要素,這在許多方面都是一種新的現象。雖然知識分子宣稱,他們打從一開始對社會就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在更早之前化身為神職人員、經文抄寫員與占卜師),不過,無論是原初化的、還是之後高度發展的宗教文化,作為神職人員的守護者,其道德與意識型態上的創新,都受限於外部權威的教條和內在所繼承的傳統。在過去,他們不是,也不可能成為自由的靈魂、心靈的冒險者。
隨著神職人員的權力在十八世紀衰退,為了填補真空,一種新的導師(mentor)興起,並受到社會關注。世俗知識分子可能是自然神論、懷疑論或無神論者,但他也可能像羅馬教宗或牧師一樣,樂於給予人們忠告。打從一開始,他們便宣布專心致志於人類的利益,目的是讓人類進步,以鼓吹自己的學說為己任。他們實現自我任命的任務,其手段比神職人員的先輩們激進很多。他們認為自己不受制於天啟宗教 1,而對於代代流傳的集體智慧、傳統思想和約定俗成的規範,他們會依照自己的判斷,決定要選擇性地遵從或全然棄絕。
隨著越來越茁壯的自信與無畏,這是人類史上頭一遭,有人出來主張他們能診斷社會的疾病,並依靠獨立的智識對症下藥;另外,不光是社會的架構,就連人類的根本習性,他們都能想出處方來加以改善。和他們擔任神職的先輩不同的是,他們服務與解釋處方的對象不是眾神,而是眾神的替代品。他們崇拜的英雄是偷了天國火種並帶到人間的普羅米修斯。
這些新興世俗知識分子最具指標性的特色,就是他們喜愛對所屬宗教及其重要人物詳加批判。這些偉大的信仰體系,對人類的貢獻或傷害有多深?那些教宗與牧師,對其宗教的戒律、貞節與真誠,還有仁慈與捐贈,實踐到什麼程度?他們對教會與神職人員的觀點非常嚴厲,而今,宗教的影響力已經持續衰退了兩百年,世俗知識分子在形塑我們的意見與制度上所扮演的角色,則是持續擴大,似乎是時候該檢驗他們在公、私領域上的經歷了。我尤其想聚焦在「告訴人類該如何處世的知識分子們」的道德與判斷力。他們自己的人生過得怎麼樣?他們對親友與夥伴誠實正直到什麼程度?他們處理情欲與財務是否公允?他們說的、寫的都是真實的嗎?以及,他們的思想體系在經歷時間與實踐的考驗後,是否還站得住腳?這項調查從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rau)開始,他在這些現代知識分子當中居首位,是他們的原型,在許多方面也是影響力最大的一位。雖然比他更年長的知識分子如伏爾泰,早已開始進行推翻聖壇與尊崇理性的工作,但盧梭是結合現代普羅米修斯所有顯著特質的第一人:主張他有權利全然反對既存秩序;自信他有能力根據他所設計的原理原則,將既存秩序改頭換面;相信這一切能透過政治手段達成;以及最特別的,他承認本能、直覺與衝動,對人類行為的影響甚鉅。他相信自己對人類有一份獨一無二的愛,並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天賦與洞察力,使他的言詞得以精彩巧妙。在他的生前身後,以他對自己的評價來看待他的人,數量出奇地多。他的影響力無論從時間遠近來看,都很巨大。在他死後的那個世代,他的地位達到神話等級。他死於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十年前,然而,當時許多人認為,促成法國大革命及歐洲舊制度 2 垮台的人就是他,路易十六與拿破崙也這麼認為。英國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曾這樣論及這場革命的菁英:「這些領袖之間曾有一場大爭執,爭著誰才是最像盧梭的那一個…… 他是他們公認最優秀的完美化身。」法國大革命時期政治家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的說法是:「盧梭是唯一一個,透過他那高尚的靈魂與高貴的品格,證實他配得上人類導師此一角色的人。」法國大革命期間,國民公會投票表決將他的遺骨移葬先賢祠。在典禮上,國民公會主席聲明:「是盧梭提升了我們的道德、習俗、法律、理解力與習性。」不過,如果拉長時間、更深一層來看,盧梭改變了作為文明人的某些基本前提,替換了人類心智的裝備。他的影響範圍非常廣泛,但可以總結為以下五個:第一個,現代教育的所有觀念,某種程度上都受到盧梭學說的影響──尤其是他一七六二年的論文《愛彌兒》(Émile)。他普及了、而且在某種程度上發明了愛國情操與戶外活動,並追求昂揚的生命力、自發性、強健的體魄與性格。他批評城市的世故,看出文明的造作,並給予惡名。他發明了冷水澡、計畫性鍛鍊、磨練心性的體育活動,以及週末度假別墅。
第二個是關於他對自然的重新評價。盧梭教導人們,不要信任緩慢進展的物質文化所帶來的漸進式進步。基於此,他屏棄過去參與的啟蒙運動,尋求更徹底的解決方案。他堅信「理性」作為一種診斷社會的工具,有嚴重的侷限性。然而,這並不表示人類心智無法實現必要的改變,因為大腦還有富於想像力的深刻觀察力與直覺,這種潛藏的、尚未被開發利用的資源,必須用來強制改變再也起不了支配作用的理性。為此,盧梭寫下《懺悔錄》(Confessions),該書完成於一七七○年,但直到他過世才出版。這便是第三點,他同時處理了浪漫主義運動與現代主義的內省文學,在這當中他發現自我、挖掘內在,並供大眾檢驗,這是繼文藝復興成就之後的更上層樓,是讀者首度看見作家的內心世界(這也是現代文學的一大特點)。雖然如此,這卻是騙人的版本,他的內心因此顯現出欺人的一面,表面坦白,實則充滿奸詐。
盧梭的第四個普及化概念,在某些方面來說,是最具滲透力的。他認為,當社會從大自然的純樸狀態逐漸發展為城市的複雜世故之後,人類也變得邪惡汙濁:在人類自私天性中,他所謂的自愛(amourdesoi)會轉變成更邪惡的本能──由虛榮與自尊組合而成的自私(amour-propre)。每個人的自我評價都來自別人對自身的看法,人們將因而尋求金錢、力量、智力與道德上的優越,使他人欽佩自己。人類天性中的自私將變得爭強好鬥、貪得無厭,不但變得與其他人(因視為競爭者而非夥伴)疏離,也跟自己疏離。疏離會引發心理疾病,特徵是外在與現實之間不幸的背離。
在盧梭看來,競爭之惡會摧毀一個人天生的群體感,並激發他全部的劣性,包括渴望利用別人,這讓盧梭質疑財產私有制,認為這是社會犯罪的根源。所以,他的第五個創新,是他在工業革命的前夕,發展出批判資本主義的要素,這同時可見於他的劇作《納西瑟斯》(Narcisse)與演講集《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Discoursur l’egalite)。他為資產下定義,並認為透過競爭獲取資產,是引起疏離的主因。盧梭為後人留下的思想寶藏,以及他對於文化演進的相關想法,後來受到馬克思等人的攫取繼承。對他來說,「自然」指的是「原始」或「文化出現以前」,由於個人與他人的關係會誘發人類的邪惡傾向,因此所有文化都會帶來弊端:如同他在《愛彌兒》中所寫,「一個人所吐出來的氣息,對其同胞是致命的」。因此,人類文化本身便是一個會不斷發展的人造結構,會規範人們的行為舉止,而你可以透過改變文化,同時改變產生這些文化的競爭因素,確實又徹底地改善人類的行為──這得靠社會工程(socialengineering)。
盧梭要建構的這些概念是如此廣泛,幾乎光是概念本身,便是現代思潮的百科全書。當然,這些概念並非全都出自盧梭。他博覽名家:笛卡爾、拉伯雷(Rabelais)、巴斯卡(Pascal)、萊布尼茲(Leibnitz)、貝爾(Bayle)、豐特奈爾(Fontenelle)、高乃伊(Corneille)、佩托拉克(Petrach)、塔索(Tasso),以及他尤其喜愛引述的兩位哲學家,洛克(Locke)與蒙田(Montaigne)。德.斯戴爾夫人(Germaine de Staël)認為盧梭有著「最令人崇敬的稟賦」,她表示:「他沒有發明任何東西,不過,他為一切點燃了火苗。」更確切地說,簡單、直接、有力與發自內心的熱情,讓盧梭作品中的見解,看起來多麼生動又清新,許多讀者因此大開眼界。
於是,這個人成為了擁有卓越力量的道德與智慧導師。而他又是怎麼得到這些的呢?盧梭是瑞士人,在日內瓦出生,被養育成一個喀爾文主義者。其父艾薩克(Isaac)是製錶商,但生意並不太好,反而經常惹是生非,頻繁涉入暴力與暴動。其母蘇珊娜(Suzanne Bernard)則出身富裕家庭,但生下盧梭之後沒多久,就因為產褥熱而過世。儘管他雙親都不是來自於統治日內瓦的寡頭政府,或是與二百人理事會(Council of Two Hundred)、二十五人內部理事會(Inner Council of Twenty-Five)關係緊密的家族,但他們享有最高的投票權與法律上的特權,盧梭也一直都很清楚自己的優越地位,這使他出於利益(而非出於智識的信念)自然而然成為保守派,也使他終其一生,都藐視沒有投票權的群眾。他的家境也算是不錯。
盧梭沒有姐妹,但有一個大他七歲的哥哥。由於盧梭長得像母親,痛失妻子的艾薩克特別疼愛他。艾薩克對他的態度,擺盪於哀憐的情感與恐怖的暴力之間,但即便他受寵,卻曾經公開譴責艾薩克扶養他長大的方式,他後來在《愛彌兒》中寫道:「為人父者的野心、貪欲、專橫與錯誤的先入為主,還有他們的疏忽與殘酷的無動於衷,比起為人母者欠缺思慮的心軟,對孩子的造成傷害更勝百倍。」不過,父親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是哥哥,他在一七一八年,因為父親的請求被送入少年感化院,理由是屢教不改。一七二三年,他逃走了,就此音訊全無。盧梭於是成了實質上的獨子,他對許多當代的知識分子領袖就是這麼說的。不過,儘管多少會覺得自己幸運,但他從孩提時期便有強烈的被剝奪感,以及自哀自憐──後者或許是他最為人所知的個人特質。
……
在盧梭的自憐背後,是令人難以忍受的自大,他認為自己所受的苦、自己的本質,都不同於凡夫俗子。他曾經寫過,「你的不幸怎麼可能跟我一樣?我的處境舉世罕見,從古至今沒聽說過」、「平心而論,能愛我如我愛自己的那個人,還沒出生」、「沒人比我更有愛的天分」、「我生來就是實際存在過最好的朋友」、「如果我認識比我更好的人,我會疑懼不安地離開人世」、「你找給我看看,有誰比我更好、更忠誠、心更軟、更多愁善感」、「後代子孫會尊敬我…… 因為我值得」、「我對自己深感欣喜」、「我的慰藉存在於我的自尊」、「如果歐洲找得到一個開明政府,他們會設立我的雕像」。難怪伯克會說:「自負只是他的瘋狂行徑中,程度最輕微的小缺點。」
盧梭的自負,有部分是出於他認為自己的基本情緒運作不太正常。「我感覺自己優秀到不會有恨」、「我太愛自己了,以至我無法恨任何人」、「我從來不知道憤恨是什麼感覺,嫉妒、惡意、報復未嘗進駐我心…… 偶爾生氣,但我從來不狡猾或積怨」。實際上,他常常積怨,而且狡猾地追逐這些憤恨,很多人也注意到這一點。盧梭是第一位公開表明自己是所有人類之友的知識分子,而且他多次這樣表明。但他所說的愛,是泛指全人類,他培養出一種強烈癖好,喜歡譴責特定的個人。他早先的友人,日內瓦的特羅尚醫師就是其中一名受害者,特羅尚曾提出質疑:「全人類之友怎麼會沒朋友,或幾乎沒有?」盧梭的回應,是捍衛他自己有權決定誰值得鞭策:「我是人類之友,人類到處都有。真誠之友還會發現,惡意到處都有──我其實不用說得太多。」身為一個自我中心的人,盧梭有點把對他本人的敵意,視同對真實與美德的敵意。因此他對敵人做什麼都不是壞事,這些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此學說的永恆懲罰。他告訴艾丕內夫人:「我本性並不殘忍,可是當我看到這個世界沒有公正地對待這些惡人,就覺得一定有一座地獄正等著他們。」
既然盧梭如此自負、自我中心又愛吵架,為何還有這麼多人等著跟他交朋友?這個問題的答案,會帶領我們來到他的性格特質與歷史意義的核心。這有一部分出於偶然,一部分出於本能,一部分是精心策畫的計謀。他是第一位計畫性地利用特權階級罪惡感的知識分子,而他確實達成了目的,以一種前所未見的新方法:系統地讚揚「失禮」。他是現代社會中某種性格小生的原型──憤怒青年。他的本性並不反社會,他小時候確實希望在社會上發光發熱。他特別想得到上流社會婦女的青睞,他寫道:「女裁縫師、女服務生、女店員不會打動我。我需要的是年輕的貴婦。」不過顯而易見的是,他是個改變不了的鄉巴佬,在許多方面都粗魯無文。他在一七四○年代開始嘗試打入上流社會,試著學習上流社會的遊戲,卻徹底失敗。他那時第一次嘗試勾搭一位已婚貴婦,結果臉丟大了。
……
這種精神錯亂所造成的心智極度痛苦,對患病者來說非常真實,有時也不得不同情盧梭。遺憾的是,他無法因此退出舞台。他是在世時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他以人類之友自居,尤其是真實與美德的鬥士,他這樣的形象在過去廣受歡迎,現在也確實如此。所以,把他看作真實與美德的敘述者,我們有必要更仔細觀察他的行為。我們發現了什麼?真實的議題尤其重要,因為盧梭死後,最知名的就是他的《懺悔錄》。這一部著作努力自我剖析,訴說一個人一生的內在真相,這種嘗試亙古未有。這本書是極端坦率的新類型自傳,就像詹姆士.包斯威爾(James Boswell)晚十年才出版的《約翰遜傳》(The life of Dr Johnson),是一種極端精確的新類型自傳。
盧梭宣告這本書真實不欺。他在一七七○年至一七七一年的冬天為此書舉辦朗讀會,在擠滿人的沙龍裡持續了十五至十七個小時,現場還提供麵包。他攻擊他的受害者們,但他的論點令人忍無可忍,以至於其中一個受害者:艾丕內夫人,要求當局必須阻止朗讀會的進行。盧梭同意停止,卻在最後一次朗讀會加入以下談話:「我必須說真話。如果有任何人所知道的事實,與我方才說的話相反,就算檢驗上千次,那也是謊言跟詐欺…… 無論是誰,以他的眼光來審度我的天性,我的性格、品行、傾向、消遣、習慣,據以認定我是個不誠實的人,他本人就該被勒死。」這番話帶來了一陣令人難忘的沉默。
盧梭之所以能打著「說真話」的名號,是靠宣稱自己的記憶力一流。更重要的是,他說服讀者自己很誠懇,因為他是第一個公開性生活細節的人。他沒吹噓自己很勇猛,反而滿是羞愧與不情願。恰如他說的,他提到他的性經驗是「黑暗又骯髒的迷宮,最難啟齒的不是罪惡,卻是讓我們覺得荒謬與羞愧的事」。可是一個真誠不造作的人,要如何違背自己的意願呢?身為一個年輕人,他在義大利杜林(Turin)幽暗的後街嘶吼,向女人露出光溜溜的屁股。「在她們露出很難形容的眼神之前,露屁股讓我得到愚蠢的歡愉。」盧梭是天生的暴露狂,性方面如此,其他方面也是,而且確實有講述自己性生活的癖好。他描述他的性受虐狂,說他被牧師的妹妹──嚴格的朗拜爾西耶小姐(Mademoiselle Lambercier)打屁股是何等享受(為了激怒她處罰,他還故意搗蛋)。還有他如何慫恿女校友格羅頓小姐(Mademoiselle Groton)也打他屁股:「向一位我拜倒在裙下的傲慢情婦撒謊,服從她的命令,請求她的原諒──對我而言真是賞心樂事。」他告訴大家年少時自己如何手淫,他辯護道,這能讓年輕人免於染上性病,而且「此一令人感到恥辱羞愧的罪行,取得是如此便利,對生活的想像擁有不只一種吸引力:這能讓所有的女人臣服於他們一時的興致,不需美女們的同意,就能讓她們想要誘惑他們,滿足他們。」他描述在杜林的旅店,有同性戀者意圖誘惑他。他坦承與華倫夫人還有她的園丁玩三人行。他形容,當他發現有個女孩有一側乳房沒乳頭時,他無法與她做愛並暴怒離去:「我撇下女人去算數學。」他坦承日後又開始手淫,因為這比積極追求感情生活方便多了。有點故意,又有點下意識地,他給人一種印象:他對性的態度一直都很孩子氣。他的情婦華倫夫人,永遠都被他稱作「媽媽」。
這種有害的自白增強了大家對他「尊重真相」的信心,接著,他再藉由牽扯其他丟臉、與性交無關的插曲來強化這種印象,包含竊盜、謊言、懦弱與擅離職守。不過當中有狡詐之處。他的自我控訴,讓他後來控訴敵人時更有說服力。如同狄德羅憤怒的評論:「他用令人厭惡的方式描繪自己,給他不公正又殘酷的指責批上了真相的外衣。」還有,這些自我控訴都是假的,因為每一次自我批判,後面都會加上毫無遮掩的認錯,再巧妙地辯白自己無罪,讓人讀到最後對他產生同情,又為他的坦率加分。然後再一次,盧梭呈現出來的真相往往變成半真半假的陳述。選擇性誠實,某種程度來說是最不誠實的,這一再出現在《懺悔錄》與他的書信裡。有些「事實」他承認地如此乾脆,但依照現代的學術研究,幾乎都經過歪曲或者根本不存在,有些就算用他的內部證據來看也很明顯。例如,他說同性戀對他獻殷勤的說法,就有兩種相當不同的版本,分別在《愛彌兒》與《懺悔錄》裡。他的「全面記憶」是一個謎,父親過世給錯年分,並說父親當時「大約六十歲」,實際上他父親活到七十五歲。他對杜林旅店所有交代的細節,幾乎都是謊言,但這是他少年時最關鍵的事件之一。而如果透過外部證據,則《懺悔錄》中無一句可信,且真相呼之欲出。實在很難不認同最了解盧梭的當代評論家約翰.赫伊津哈,他指出,由於《懺悔錄》堅稱內容真實可信,使得其中的歪曲事實與謊言特別可恥:「一個人越是專注地一讀再讀,越是深入鑽研,就越能看這本書可恥的更多層面。」什麼讓盧梭的不誠實變得如此危險,又讓他的杜撰震懾了他從前的朋友們──是他用來描述那些人的高超、邪惡的技巧。如同他公正的傳記作者克勞克教授所言:「他跟別人吵架的敘述(好比他在威尼斯發生的事)有種難以抗拒的說服力、口才與真摯的感情。知道真相之後會很錯愕。」
既然盧梭以這種方式獻身於真實,我們又該如何看待他的美德呢?很少有人的生活必須承受如此近距離的監督,近乎赤裸裸地躺在數以千計的學者面前接受道德審判。但考量到他的主張、他在道德標準與行為方面上的持續影響,這也是不得已的事。他說,自己是個為愛而生的人,他傳授愛的學說,比大多數傳教士更不屈不撓。那麼,他是如何靠他那些被研究得一清二楚的天性,來表達自身的愛?從出生時,死亡便奪走了盧梭的母親與正常家庭生活。既然不認識,或許他對母親沒什麼感覺,但他對其他家人也沒有展現過真正的關懷或關心。父親對他來說沒有意義,父喪只是一個繼承財產的機會。在這一點上,盧梭對他長期失聯的哥哥的關心,也只是為了看對方還在不在人世,這樣家族財產才會都落入他手中。他把他的家庭視為現金的一種形式。在《懺悔錄》裡,他描述:「我有個顯而易見的矛盾──極其蔑視金錢,卻又對它有著近乎齷齪的貪念。」他畢生沒有留下太多蔑視金錢的證據。當他的家族財產證實由他繼承,他描述自己收到匯票時,盡了最大的意志力,拖到隔天才把信件打開。他說:「我刻意慢慢打開,找到裡面的匯票。我馬上覺得心情舒暢,但我發誓我最渴望的是戰勝我自己。」
如果這是他對原生家庭的態度,那他又會怎麼對待他實質上的養母華倫夫人呢?答案是:小氣吝嗇。華倫夫人在盧梭窮困時至少出手接濟四次,但盧梭後來飛黃騰達、華倫夫人生計艱難時,他卻甚少幫她一把。根據他自己的敘述,他一七四○年代繼承家族財產時寄了「一點」錢給她,但拒絕繼續寄錢,因為錢會被她身邊的「無賴們」拿走。這只是藉口,她後來好幾次懇求盧梭幫忙,卻都石沉大海。華倫夫人最後兩年臥病在床,死於一七六一年,死因可能是營養失調。夏美伯爵(Comte de Charmette)同時認識兩人,強烈譴責盧梭沒有「至少把一部分的錢,還給對他最慷慨的女贊助人」。盧梭後來繼續應付華倫夫人,在《懺悔錄》裡,以高明的詭計讚揚她是「最好的女人與母親」,說自己沒寫信給她,是因為不想一一細數自己的困難讓她難過。最後他說:「去吧,品嘗妳的慷慨所結下的果實,為妳的子弟們準備好一個他希望有天能逃向妳的地方!要為妳的不幸開心,因為天國終結了不幸,為妳解除了他的痛苦景況。」以純粹的自我中心來看待她的死亡,這正是典型的盧梭。
要是沒有這強烈的自我中心,盧梭能愛一個女人嗎?根據他自己的說法,「我的初戀與畢生唯一的愛,是蘇菲(Sophie)」。蘇菲是烏德托公爵夫人(Comtesse de d’Houdetot),也是他的資助人艾丕內夫人的姻親。或許盧梭愛過她,但他說自己寫情書給對方「採取了預防措施」,如此一來,如果信件曝了光,對她的殺傷力將不亞於他本身。而泰蕾茲.勒瓦瑟,這名二十三歲的洗衣女在一七四五年成為他的女傭,和他在一起三十三年,直到他過世。他說自己「從未感覺對她有半點愛…… 我在她身上滿足了性需求,是純粹的性,與她個人無關」。他寫道:「我跟她說過,絕對不會離開她,也絕對不會娶她。」二十五年之後,盧梭和她辦了假結婚,只有幾位朋友到場觀禮,而且婚禮被用來發表一段非常自負的演說。盧梭斷言後代子孫會為他豎立雕像,以及「與盧梭為友,將不只是一個虛名」。
某種程度上,他瞧不起泰蕾茲是做粗活、目不識字的女傭,也鄙視自己是她的伴侶。他控訴,泰蕾茲的母親非常貪婪,而她的兄弟偷了他四十二件上等襯衫(沒有證據顯示她家人有這麼壞)。他說泰蕾茲不只無法讀寫,也不會看時鐘跟日期。他從沒帶她出門過,他如果邀請朋友到家裡吃飯,她也不能同席。她負責送來食物,然後盧梭會「拿她找樂子」。為了討盧森堡公爵夫人開心,他編寫了一張泰蕾茲失禮行為的列表,就連一些出身高貴的朋友,看到他如此輕蔑的態度也大感錯愕。同時代的人都把盧梭跟泰蕾茲切割開,有些人以為她是用來中傷他的小道消息。無數個將盧梭偶像化的傳記作者,無所不用其極地抹黑她,以漂白他對她心胸狹隘的種種行為。
確實,公平一點來看,盧梭也曾經讚美泰蕾茲「擁有天使般的心腸」、「溫柔體貼又善良」,是個「絕佳的商量對象」、「心思單純且不會賣弄風騷的女孩」。他所認識的她「膽小又好掌控」。事實上,我們不知道盧梭是否真的了解泰蕾茲,或許他太過自戀,根本沒心思對泰蕾茲好好觀察研究。有關她最可靠的描述,是詹姆士.包斯威爾提供的,他曾在一七六四年五次拜訪盧梭,後來還護送泰蕾茲到英格蘭。他所認識的泰蕾茲「是個嬌小、活潑、俐落的法國女孩」,包斯威爾為了更近一步接近盧梭而收買她,並設法向她討到兩封盧梭寫給她的信(目前僅存一封)。信件顯示出盧梭的關愛,還有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她告訴包斯威爾:「我與盧梭先生已經在一起二十二年了。我不會放棄法國王后的寶座。」另一方面,包斯威爾曾是她的旅伴,他毫不費力就引誘她上床。包斯威爾在手寫的日記原稿上詳述此一風流韻事,後來被他的遺稿執行者剪下來,在空白處標注「這一段該受指責」,但漏了一句,是他在多佛時寫的:「昨日一大清早離開她的床鋪(在樓梯平台),又做了一次:一共十三次。」而且其他保留下來的陳述,都足以顯示這個女人比大多數人所認為的更世故、更老練。事實似乎是她以一種敬愛的方式獻身盧梭,卻被盧梭的行為教育成要利用他,正如他對她的利用。盧梭最溫暖的愛都給了動物,包斯威爾記錄了一個愉悅的場景,盧梭跟他的貓還一隻叫蘇丹(Sultan)的狗嬉戲。他給予蘇丹(還有上一隻狗,叫土耳其)的愛是 在其他人身上見不到的。蘇丹非常愛亂叫,盧梭帶牠前往倫敦時,還差點因此無法參加加里克為他安排在皇家劇院的特別義演。
盧梭留下泰蕾茲,甚至有些珍惜她,因為她能為他做的事情,動物做不到:例如為他接上導尿管。他可能無法容忍有第三者介入他們的關係。例如,有個出版商寄給她連衣裙,他勃然大怒,立刻否決了要支付給她退休金的計畫,這計畫或許能讓她在經濟上不再仰賴他。最重要的是,他不允許孩子占走他對泰蕾茲的各種權利,這導致了他最大的罪行。由於盧梭很大一部分的聲望,是因為他教養孩童的理論──主要是教育,在他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愛彌兒》與《社會契約論》,甚至在《新愛洛伊斯》中都有著墨。奇怪的是,他的現實生活與筆下的相反,他不怎麼關心小孩,也沒有任何證據表示他曾經做研究來驗證理論。他說沒人比他更愛與孩子們玩了,但有一則相關的傳聞,顯示出他這方面的能力其實令人不安。畫家德拉克拉瓦(Delacroix)在《日誌》(Journal)表示曾有個人告訴他,說在杜樂麗花園(Tuileries)瞧見盧梭:「一個孩子的球打中這位哲學家的腿。他暴怒,用手杖追打那個孩子。」就我們對盧梭個性的認識,他也不太可能成為一個好父親。即便如此,如果知道盧梭對親生子女做了什麼事之後,你可能會驚訝地作嘔。
一七四六年至一七四七年的冬天,泰蕾茲第一個孩子出世,我們不知道性別,因為他沒有獲得名字。盧梭說,他以「全世界最大的困難」說服泰蕾茲必須棄養,「以保全她的名聲」,她「嘆息一聲,照他的話做了」。盧梭在嬰兒衣服裡放了一張密碼字卡,要助產士把襁褓中的嬰兒丟在育嬰院。他跟泰蕾茲後來生的四個小孩也是以相同方式棄養,只有第一個還不嫌費事地寫了張密碼字卡。他也都沒有幫小孩取名。這些嬰兒不可能倖存太久,一七四六年的文學刊物《法蘭西信使》(Mercure de France)中有該機構的沿革,表明當地每年有超過三千個棄嬰,已經窮於應付。盧梭自己在一七五八年也記錄,棄嬰總數當時已攀升到五千零八十二個,到了一七七二年,平均數量已接近八千。有三分之二的棄嬰未滿週歲就夭折了,每一百個棄嬰中,平均有十四個能活到七歲,有五個能活到成年,而且多數都將成為乞丐或無業遊民。盧梭甚至沒記錄他這五個孩子的出生日期,對孩子後來的生活也漠不關心,除了在一七六一年,他有次以為泰蕾茲快死了,於是做了敷衍的嘗試,想用密碼打探第一個孩子的下落,但也很快就不了了之。
盧梭無法將自己的情形徹底保密,例如一七五一年與一七六一年,他偶然以私人信件來為自己辯護。而在一七六四年,伏爾泰因為盧梭攻擊他的無神論而被激怒,結果伏爾泰假冒成一名日內瓦牧師,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書名是《公民的情感》(LeSentimentdesCitoyens)。該書公然指控他遺棄了五個子女,並且描述他身染梅毒,是個殺人兇手。但盧梭對這些指控的否認,大致上被公眾接受了。無論如何,他對這段往事的思考,只是他寫《懺悔錄》的因素之一而已。他寫這本書的本意,是想為那些已公諸於世的事實,進行反駁或脫罪。他在書中兩次為棄養之事辯解,然後繼續在《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與許多不同的書信中回應。他公開或私下努力為自己平反,時 間長達二十五年,留下的文字相當多,但他只是提油滅火,因為這些訊息是由惡毒的言語與偽善所包裝的自私組合而成。他先是指責不信神的知識分子這個邪惡的小圈子,說裡頭人強加了「孤兒」的概念在他天真的腦中,接著說養育子女「多有不便」。他養不起。「當我簡陋的閣樓被家務與孩子的吵鬧聲填滿,我要如何得到工作所需的平靜?」他或許要被迫卑躬屈膝,去做降低他格調的工作,「所有這些不名譽的行為,讓恐怖合情合理地淹沒我」。「我很清楚,如果我當爸爸的話,那不會有比我更慈愛的父親」,但他不要他的孩子與泰蕾茲的母親有任何接觸:「把我的孩子交託給那個沒教養的家庭,這想法令我擔憂。」至於殘忍,像他道德如此超然之人,怎麼可能會犯下這種罪行?「…… 我愛偉大、真實、美與正義熱烈。我害怕每一種罪惡,我不具有怨恨或傷害他人的能力,甚至連想過都沒有。當我所見皆是善良、寬厚與親切,我便感受到愉快與雀躍。我問,同樣的這一顆心,有可能墮落自此,把最甜蜜的義務踩在腳底下?不!我感覺到,而且大聲宣告──不可能!盧梭此生哪怕只有一個瞬間,都不可能是個沒血沒淚、沒同情心,或是不近人情的父親。」
為了維護他的美德,盧梭不得不持續下去,正面地為自己辯護。就這點來說,盧梭幾乎是湊巧把我們引入他私人問題與政治理念這兩方面的核心。我們對盧梭拋棄孩子正確性的描述,不光因為這是他殘忍無情的顯著案例,也因為這過程中的重要環節,產生了他對政治與政府角色的理論。盧梭認為自己是被拋棄的孩子,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從未真正長大,終其一生都無法自立。他把華倫夫人當母親來求助,把泰蕾茲當成保母。《懺悔錄》中有許多篇幅、他的書信中有更多篇幅強調孩子的要素,許多與他往來過的人都把他看成小孩(例如休謨)。這些人剛開始把他看作一個無害又聽話的孩童,接著發現自己努力操控的,是一個天才橫溢、兇狠殘暴的少年罪犯。某些方面,盧梭也自覺是孩子,所以他無法養育小孩。必須有些東西可以取代他的位置,而那個東西就是國家,以孤兒院的形式替他做事。
所以,他主張他的所作所為是「良善且明智的安排」,是柏拉圖所倡議的。「養小孩最好不要太小心,這能讓他們更強健。」他寫道:「我曾希望,直到現在也是如此希望,自己可以像他們那樣被撫養長大。要是我有相同的幸運就好了。」簡言之,他把責任轉移給政府,「我認為我在演一齣公民與父親的戲,把自己看成柏拉圖共和國裡的成員」。
盧梭聲稱,他思索自己對待小孩的處理方式,最終讓他的教育理論成形,然後在《愛彌兒》中介紹推演展,還幫他發想出同年出版的《社會契約論》。在這個特殊情況下,他為了自我辯護的重申與自負變得更加堅定(過程是一連串輕率、缺乏思慮的藉口,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他一開始就知道自己的行為是不自然的),接著逐漸演變成發自內心的信念,主張教育是改善社會與道德的關鍵。因此,這是國家大事。政府必須塑造所有人的想法,不光是孩童(正如他在孤兒院的棄子),也包括成年公民。透過這難以理解又無恥的連環扣,盧梭為人父的惡劣行徑,被連結上他的意識形態產物:未來的極權主義政府。
盧梭的政治理念總是圍繞著混亂,因為在許多方面,他都是個前後矛盾而對立的作家──盧梭「產業」變得如此龐大,理由之一是為了解決「問題」而蓬勃發展的學術研究。他的著作中有些段落,使他看起來守舊,強烈反對革命,他寫道「試想要這麼大刀闊斧的危險」、「投身革命的人,其結局差不多都是把自己交給增加那肩上重擔的撒旦」、「我不願與策畫革命扯上任何關係,這麼做總是導致動亂失序、暴力與流血」、「全體人類的自由權,比不上任何一個個體的生命價值」。他的著作也滿是激進的忿忿不平,「我痛恨大人物,我恨他們的地位優越、講話難聽、心存偏見、器量狹小,恨他們所有的不道德行為」。他寫給某位貴婦的信中說:「富人階級,即妳所在的階級,偷走了我後代子孫的麵包。」他自己承認,「如果那些富人與成功人士獲得財富與幸福的方式會讓我吃虧,那就會激怒我」,富人是「飢渴的狼,一旦嚐過人類的鮮血,就拒絕其他食物」。他有許多威猛的格言,激進的口吻讓他的著作特別受年輕人喜歡。「土地所產出的果實屬於我們全體,土地不歸任何人所有」、「人生而自由,但處處都是限制」。他參與編撰《百科全書》7 的「政治經濟」部分,他對統治階級的總結如下:「你需要我,因為我富你窮。讓我們達成這樣的協議:我將允許你擁有為我服務的榮耀,我命令你提供什麼,你就要把你的所有給我,除了麻煩以外。」
【評論:double think】
不過,只要我們了解盧梭希望建立的國家本質,他的論點就會變得前後一致了。以一種截然不同、本質是平等主義的東西來取代現有社會是必要的,但在過程中,不容許革命帶來的動亂失序。富裕與特權階級應該被國家取代,體現公共意志(General Will),而公共意志訂下的所有契約都得遵守。由於國家透過系統化的文化工程處理程序,對所有人反覆灌輸美德,因此服從將變得本能且自願。國家是父親,是祖國,全體公民都是慈父般的孤兒院的子女。(約翰遜博士寫了令人費解的評論,但他戳破了盧梭的詭辯,「愛國主義是壞人最後的避難所」。)不像盧梭自己的孩子,「公民子女」是透過自由訂定契約,來把自己交給國家/孤兒院,因此,他們的集體意志構成了合法性,有不被強迫做任何事的權利,要是國家想要制定什麼法律,那必須要是他們熱愛且願意服從的。
儘管盧梭寫了與公共意志相關的自由權,但權威機構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這也是列寧(Lenin)民主中央集權主義的早期輪廓。法律須由公共意志制定,而公共意志在定義上,必須擁有道德威信。「人民為自己所立的法,不能不公不義」、「公共意志永遠公正」。此外,假如國家的動機良好(也就是有令人嚮往的長期目標),那公共意志就能可靠地交給領袖們來好好解釋,因為「他們知道公共意志會偏愛最符合大眾需求的決策」。所有人都會發現,與公共意志作對是錯的:「當公共意志與我自己的觀點相反時,就單純證明我錯了,我以為我所想的就是公共意志,但其實不是。」更確切地說,「如果有一天我獨特的意見被接受,我就走到我先前意志的反面,而我將不再自由」。這種說法,讓我們幾乎是身處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的反共小說《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中的寒冷地帶,或是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描述的「新話」。
【評論:程序是按照代碼寫的方式執行,而不是按照寫代碼的人的想的方式。】
盧梭的國家概念不單單是獨裁主義,還是極權主義,因為它指揮人類活動的每一面向,包括思想。在社會契約之下,個人被迫「讓出本身的所有權利給全體社會(即國家)」。盧梭認為,在人類天生的自私與社會責任之間、自然人(Man)與公民(Citizen)之間,有著根深蒂固的衝突,這令他痛苦。社會契約的功能與國家的作用,就是讓自然人再度變得完整:「讓人能做完整的自我,他想要多快樂,你就能讓他就有多快樂。讓他把一切給予國家,或者讓他一個人保留一切。但如果你讓他的心分歧,就是把他撕裂成兩半。」所以,你必須待公民如孩童,控制他們的成長與思想,「在他們心底種下社會法則的種子」。然後他們便會成為「合乎理性的社會人,以及同意被這樣對待的公民。他們將會完整如一,會令人滿意,會幸福,而他們的幸福即是共和國的幸福」。
這個過程需要全然的屈從。一開始,他為科西嘉島起草的憲法所規畫的社會契約宣言,誓詞是這樣寫的:「我把我本人,軀體、道德、意志以及我所有的權力,交接給科西嘉國,同意她之於我的所有權,包括我自己還有依靠我的所有人。」於是乎,國家「握有人民及他們所有的權力」,可以控制他們經濟與社會生活的每一面向,打造紀律、反對奢靡與都市化,人民除非經過特別允許,否則禁止進入城鎮。盧梭以幾種手段為科西嘉規畫的政府,成為波爾布特在柬埔寨嘗試建立的政權的先軀。這完全不意外,因為巴黎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政治領袖,全都吸收了盧梭的概念。當然,盧梭由衷地相信這種國家會令人滿意,因為人民將被訓練成愛國分子,也喜歡這種國家。他沒使用「洗腦」這樣的字眼,但他寫道:「控制人民的輿論,就能控制他們的行為。」這種控制的基礎在於,將公民當作國家的孩子對待,從嬰兒時期開始,就訓練他們「想到自己時,只會想到他們與國家共同體的關係」。「讓他們除了國家之外一無所有,他們就會只為國家而不為其他。國家會取得他們的全部,也會成為他們的全部。」再一次,這為義大利墨索里尼(Mussolini)的極權法西斯主義開了先例:「萬事皆在國家之內,無一事在國家之外,沒有事物對抗國家。」因此,教育過程是文化工程的成功關鍵,讓國家受到認同,達成目的。盧梭理念的核心在「公民是孩子,國家是父母」,而且他堅持政府必須全權掌控所有孩子的養育。從此以後(這正是盧梭的概念所引發的真正革命),他透過制定法律,撼動政治的處理程序,把政治程序帶入人類存在的核心,成為新的救世主,透過產生「新人類」來解決所有的人類問題。他寫道:「萬事萬物的根本都依賴政治。」美德是有效政府的產物,「一個自然人的罪行,不超過一個受到拙劣管理的人」;「政治程序,以及新形態政府的生成,是人類疾病的完整處方」。政治將解決一切。盧梭為這個二十世紀最主要的愚蠢謬見,畫出了一幅藍圖。
盧梭在世時的聲譽,以及他死後的影響力,帶起了有關人性易受欺騙的惱人疑問,更確切地說,人在看到自己不想承認的證據時會有排斥傾向。盧梭的著作之所以受到認可,絕大部分是靠他大力宣稱自己不但正直善良,還是當代最正直善良的人。不過,當他的軟弱與罪行開始為人所知,還成為國際上的話題時,為什麼這種荒謬而無恥的宣示沒有被數落,甚至擊垮?攻擊他的人,沒有陌生人或政治對手,反而全都是過去特地向他伸出援手的友人和夥伴。他們是來真的,所做的集體控訴極具殺傷力,休謨一度覺得他「仁慈、謙和、親切、無私且極度善感」,但深入了解之後,盧梭無疑是「殘忍兇惡的人,把自己視為全宇宙最重要的存在」。狄德羅在日久年深的往來後,總結他「愛騙人、像撒旦一樣自負、忘恩負義、尖酸刻薄又滿腹惡意」。對格林來說,他「令人作嘔,毛骨悚然」。對伏爾泰來說,他「是個自負又卑劣的怪物」。這些評價中最可悲的,莫過於好心幫助他的女人們,例如艾丕內夫人與她的丈夫,她對盧梭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對你除了同情沒別的了。」這些評價不光是基於這個人的言詞,還包括他的作為,而且從那時起的兩百年間,學者們挖掘出大量的材料,無情地證實了這些人說的都是真的。有一位當代大學教授條列出盧梭的缺點:他是「性受虐待狂、暴露狂、神經衰弱、憂鬱症患者、手淫者、因一再被撤職的痛苦而產生典型衝動欲望的潛在同性戀者,無法給予正常愛情或親情,天生的偏執狂,因自身疾病成為孤僻的內向自我崇拜者,滿懷罪惡感,病態的膽怯,有偷竊癖,是幼稚病(infantilist)的患者,急躁易怒,又吝嗇貪婪」。
這類的指控,以及大量出現的佐證,並未改變太多世人對盧梭及其作品的尊敬,反倒支持他在智識與情感上的魅力。終其一生,無論他跟多少朋友撕破臉,對他來說,交新朋友、獲得新的仰慕、信徒,讓達官顯貴給他華宅、晚宴與他所渴求的恭維,都不會是難事。他死後葬在埃爾芒翁維爾(Ermenonville)湖上的白楊島(Île des Peupliers),這裡很快就變成全歐洲的男男女女世俗的朝聖地。那裡有如中世紀聖徒的聖陵。對於此地「虔誠」的滑稽描述,讀來可笑:「我雙膝下跪…… 雙唇壓在冰冷的紀念碑上…… 然後親了一次又一次。」他的遺物,例如菸草袋與菸草罐,被小心存放在大家都知道的「聖所」內。這讓人想起人文主義先驅伊拉斯謨(Erasmus)和約翰.科利特(John Colet)在一五一二年造訪聖托馬斯.貝克特(Saint Thomasà Becket)的大聖堂,然後輕蔑地嘲笑著絡繹不絕的朝聖者。他們要如何形容「聖盧梭」?──法國小說家喬治.桑(Georges Sand)都這麼稱呼他。這種事在宗教改革三百年之後,不是應該絕跡了嗎?盧梭的遺骸移葬先賢祠之後,對他的讚譽從未間斷過。對康德(Kant)來說,他「擁有敏銳善感、完美無比的靈魂」。對雪萊來說,他是「令人崇敬的天才」。對席勒(Schiller)來說,「他擁有基督般的靈魂,唯有亞威的天使與他作伴才相稱」。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與小說家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雨果(Hugo)與福樓拜(Flaubert),都對他深表敬意。托爾斯泰說盧梭與《福音書》(Gospel)「是對我人生兩大有益的影響」。法國人類學家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Lévi-Strauss)是我們這一代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他在他最重要的著作《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裡,頌揚盧梭是「我們的大師與我們的同道…… 要不是配不上他偉大的事蹟,本書的每一頁都當奉獻給他」。
這一切都令人非常困惑,象徵著知識分子比任何人都不講道理、沒有邏輯,而且迷信。事實似乎是:盧梭是一個寫作天才,但他的觀念與生活,兩者都不幸地失衡了。為他人生寫下最佳總結的,是他口中「畢生唯一的愛」,即蘇菲.烏德托公爵夫人。她活到一八一三年,在非常年邁的時候發表了以下結論:「他的醜陋足以嚇壞我,而愛情並未讓他增添風采。但他是個可憐的傢伙,我用仁慈與溫柔待他。他是個有趣的瘋子。」
第二章 雪萊:追求「理想狀態」的絕情詩人
「他不介意任何年輕男子,只要他能接受,就可以跟他老婆上床。」 ── 利.罕特,雪萊的友人
……
不過,真相截然不同,尤其對那些把雪萊視為詩人(例如我)的任何人來說都非常不同,其中的差異大到令人不安。真相從不同的來源浮現,最重要的來源是雪萊自己的信件,它們暴露了雪萊在追求理想上極度專注,而只要有人妨礙到他,他就會不留情面、甚至殘忍地拋棄對方。他就像是盧梭──熱愛總體人類,但對待個體時往往特別殘酷。他燃燒著炙熱的愛,但那是抽象的火焰,靠近不會致命,卻容易灼傷。他把理想放在眾人之前,他的一生證明了理想也能如此無情。
……
一七七六年,亞當.魏薩普(Adam Weishaupt)在德國的英格斯塔德大學(Ingolstadt University)創立了光明會,宗旨是保衛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者。他們的目標是啟發全世界,直到(他主張的)「公侯與國家非暴力地從世界上消失,所有人類種族成為一家人,世界成為理性人的居所」。就某種意義來說,這成了雪萊永恆的目標,但他在吸收光明會內涵的同時,也熱衷於敵對陣營的攻擊性宣傳方式,尤其是阿比.巴瑞爾(Abbe Barruel)轟動社會的極端主義者小冊子《雅各賓派的歷史回顧》(Memoir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Jacobitism)。這本小冊不但攻擊光明會,還攻擊美生會(Masons)、玫瑰十字會(Rosicrucian)與猶太教徒。雪萊有好幾年沉迷於這本禁書,常常推薦給朋友一讀(他第二任妻子瑪麗在一八一八年寫《科學怪人》用過這本書)。同時,雪萊心裡還混雜著他當下與未來所閱讀的大量哥德式小說。
……
雪萊的兩性關係與財務狀況都不檢點,他和父母的關係、和妻小的關係、和朋友的關係、還有和工作夥伴與技工的關係都是混亂的,但這一切的共同分母是什麼?無疑的,除了他自己外,他沒有看見其他人觀點的能力。簡言之,他缺乏想像力。這就很奇怪了,因為想像力是他政治改革理論的核心。根據雪萊的說法,需要想像力或「智識之美」才能改變世界。由於詩人擁有最高品質的想像力,也由於詩人的想像力是所有人類才藝裡最具價值、也最有創造力的,所以他封他們為這個世界天生(儘管不被承認)的立法者。而他──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在此的想像力也許能同理全部的社會階級,包括被欺凌的農工、盧德分子 7、彼德魯暴民 8、工廠工人等他從未親眼見過的人民。他在抽象上能夠感受全體受苦受難的同胞,卻發現他顯然不可能(不是一次而是多次、上百次)讓想像力同理每天打交道的人。不論是從書商到男爵,從女傭到情婦,他就是無法看見這些人有權利、有資格在觀點上與他不同。而且,只要在衝突中他們不讓步或妥協,他就會辱罵他們。有一封雪萊寫給威廉斯的信,上頭日期是一八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完全概括了他這種想像力上的極限。信的開頭先在言詞上譴責倒楣的貝德威爾律師,接著猛烈攻擊時運更加不濟的希欽納小姐(「一個女人有著不顧一切的見識與令人敬畏的熱情,卻能冷酷不脫序地報仇…… 她受苦的日子我由衷大笑」)。信中還包括對人類的誓言──「我已做好準備,為我的國家與朋友們做任何能為他們效勞的事」。信的結尾是「也包括你,我仍然誠摯相待的好友」。而收件人威廉斯正在被欺騙,他很快就成為下一個憤怒的債主。[65]
雪萊把自己的人生奉獻給對政治進步的追求,運用他非凡的作詩天賦,卻沒察覺他配不上這種想像力。他沒有努力找出自己想幫助的人們,真實生活到底如何,然後設法改善。他寫出《告愛爾蘭人民書》(AnAddresstheIrish)時,尚未踏足那個國家,當他抵達愛爾蘭,他並未有系統地調查情況,或找出愛爾蘭人真正的想望。[66] 確切來說,他打算祕密地摧毀他們珍愛的宗教。雪萊也始終對英格蘭政治與公眾意見、後滑鐵盧時期的政府所面對的弊端與危急,保持全然的無知,不具有努力解決弊端的真心實意。他從未透過他認為這麼不可或缺的「想像力之穿透力」,去設法了解、公正地對待善意且敏銳的其他人,如愛爾蘭政治家卡斯爾雷子爵(Castlereagh)與倫敦警察廳創立者羅 伯特.皮爾爵士(SirRobertPeel)。在《暴政的面具》裡,他辱罵他們,就像他在書信中辱罵他的債主跟他拋棄的女人一樣。
雪萊無疑想要一個政治上全面改造的社會,包括消滅組織化的宗教,但他很困惑要怎麼做到這一點。有時他鼓吹非暴力的手段,有人視他為第一個真正非暴力抵制的福音傳播者,是甘地的先驅。[67] 他在《愛爾蘭演講》(IrishAddress)中寫道:「不要和武力或暴力扯上關係,真正的革命家對於意圖暴力的相關事物都有最強烈的不屑!…… 所有的祕密結社也都不好。」但雪萊偶爾會請求組織祕密團體,而且他的部分詩作,只能理解成煽動。《暴政的面具》本身是矛盾的:有一節詩(第三四○至三四四行)支持非暴力,但最著名的一節,其結尾是「你們為眾,他們為寡」,而且重複出現,以懇求起義(第一五一至一五四行,以及第三六九至三七二行)。[68] 拜倫跟雪萊一樣是反抗者,但拜倫的行動比起一個知識分子更像一個人──他一點也不認同改造社會,只相信民族自決──他非常質疑雪萊的烏托邦。雪萊的上乘詩作《尤利安和馬達洛》(JulianandMaddalo)記錄了兩人在威尼斯的冗長對話,馬達洛(拜倫)說到雪萊的政治計畫,「我想你可能會做出一套反駁 — 控制的系統/如果有人說話」,但實務上想出「這麼具啟發性的理論只是徒然」。
……
她獲得解放的方式是悲劇性的、無預警的。雪萊向來為速度痴迷,如果在二十世紀,他或許會成為賽車手或飛行員,他有一首詩《阿特拉斯的女巫》(TheWitchofAtlas),是一首宇宙旅行的歡樂讚歌。唐璜號本來就是為快速航行打造的,而雪萊把它改得更快。船身只有二十四呎長,卻配備了兩根主桅與縱帆,他和威廉斯設計了全新的上桅帆,能大幅增加風帆面積。為了再加快航行速度,拜倫的造船工程師在雪萊的要求下,重新趕製了桅桿裝配帆及索具,還有不合用的船尾與船首。現在她是一艘又快又危險的船,開起來「就像女巫」。[73] 天候惡劣時,這艘船只有三張順風用的大三角帆、一張風暴帆,而且僅能浮在水面上八公分。雪萊與威廉斯乘坐這艘改裝過的船,打算從利伏諾(Livorno)返航回萊里奇。他們在一八二二年七月八日午後天氣轉壞時啟程,而且全速前進。六點半風暴來襲,當地的義大利船隻全都趕忙返回港灣。其中有位船長說他觀測到雪萊的船陷於驚濤駭浪,卻依舊全速前進,而他請他們登上他的船,或至少把帆收起來,「否則你們會喪命的」。但兩人當中有一人(推測是雪萊)大喊「不」,然後就見他捉住同伴手臂、阻止收帆,「看起來很生氣」。唐璜號在離岸十哩處沉沒時,依舊是滿帆,兩人都溺斃了。[74]
濟慈在同一年先走一步,因為結核病長逝於羅馬;拜倫在兩年後,在希臘被他的醫師放血致死。這麼短的時間內,英語文學的閃亮時代就來到盡頭了。瑪麗帶著小畢西這位未來的準男爵(此時查爾斯已經過世)回到英格蘭,樹立起紀念雪萊的神話紀念碑,但她心靈上的創傷並未消逝。她目睹這位知識分子一生的陰暗面,也感受過理想的力量如何傷人。當有朋友看到小畢西正在學識字時,說:「我相信他未來會成為一個不凡的人。」瑪麗.雪萊突然動怒,激動地說:「我請求神,他長大後會成為一個普通的人。」
第三章 馬克思:偽造科學的災難預言家
「馬克思不信神,但他很相信自己,並讓每一個人都會為他所用。他心中盈滿的不是愛 而是仇恨,以及些許對人類的同情。」 ── 麥可.巴枯寧,無政府主義者
卡爾.馬克思(KarlMarx)對現實的大事件,以及對人類心靈所造成的衝擊,在現代知識分子中,無人能出其右。不光是因為他的觀念與方法論強烈吸引著那些不夠謹慎的腦袋,還因為他的思想建構出當今世上最大的兩個國家:俄羅斯與中國,以及許多附庸國。感覺上他有點像羅馬神學家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後者的作品在五世紀至十三世紀流傳甚廣,普及程度大於其他教會領袖,也因此在形塑中世紀的基督教國家時,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但馬克思的影響更加直接,因為他為自己設想出來的(我們將會看到)個人獨裁專政,是真的被實施了,而且讓人類蒙受難以估算的後果。實施者是他三個最主要的追隨者:列寧、史達林與毛澤東,他們在這方面非常忠於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是他那個時代(十九世紀中葉)的產物,而馬克思主義是十九世紀哲學的典型,並宣稱是符合科學的哲學。「符合科學」是馬克思表達強烈認可的用語,他習慣以此來區分他自己跟他的許多敵人。他和他的著作「符合科學」,敵方則否。他覺得自己發現了歷史中人類行為的科學解釋,近乎達爾文的演化論。他的追隨者在各自建立的國家中灌輸人民這個教條:「馬克思主義的見解是科學的,過去沒有其他主義達到這一點。」甚至影響了基礎教育與大學的所有科目。而且這種情況還擴散到非馬克思主義的世界,知識分子們(尤其是大學教授)被它的力量迷住了。其中有大量認同馬克思主義的自然科學權威,這吸引許多教師承認「馬克思主義在其學科中算是科學」,尤其是一些在不精確、或半精確的科系,如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與地理學。當然,如果是希特勒拿下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膠著的中東歐,而非史達林,然後在這個重要區域貫徹意志,他們也會主張納粹的教條符合科學,例如,他們的種族理論會在學術的掩蓋下滲透到全世界的大學校園。只是軍隊的獲勝確保了盛行的科學是馬克思主義,而非納粹主義。
所以,有關馬克思,我們必須問的第一件事是:要根據什麼(如果有的話)來研判他是一個科學家?意思是,他致力於追求的客觀知識,有多大程度是藉由對證據審慎的查探與評估?從表面上來判斷,馬克思的傳記透露他主要是個學者,他有兩條學者的血統。他的律師父親海因利希(Heinrich)本名希爾謝.哈勒維.馬克思(Hirscheha-Levi Marx),是一名研究猶太教法典《塔木德》的拉比之子。而這位拉比也是梅因斯(Mainz)著名拉比艾利沙.哈勒維(Rabbi Elieser ha-Levi of Mainz)的後代。哈樂維的兒子耶忽達.明茲(Jehuda Minz),是義大利帕多瓦塔木德學校的校長。馬克思的母親亨麗耶塔.普列斯堡(Henrietta Pressburg)也是一名拉比之女,是知名學者與賢者的後裔。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馬克思在普魯士的特里爾(Trier)出生,是家中九名子女之一,但也是唯一活到中年的兒子。他的姐妹們分別嫁給了工程師、書商與律師。這一家人是典型的中產階級,而且正在這個世界發跡,父親海因利希相當開明,被描述為「真正的十八世紀法國人,非常了解伏爾泰與盧梭」。[1] 由於普魯士在一八一六年頒布命令,禁止猶太人從事高階的法律與醫療工作,於是海因利希成為一個新教徒,讓六個孩子在一八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受洗。馬克思在十五歲時受了堅信禮,一度看起來像狂熱的基督徒,他上的是拘謹、但後來脫離教會的高中,接著是波昂大學(Bonn University),然後從這裡轉學至當時世上最好的大學:柏林大學(Berlin University)。他從未受過猶太教育也從未嘗試獲得相關知識,或是表現出對猶太人的理想有任何興趣。[2] 雖然一定會有人說,他培養出某一類學者特質,類似於那些研究猶太教法典的學者:他喜歡累積大量一知半解的研究資料,打算要做百科全書式的工作卻從未完成;他非常蔑視所有非學者的人;以及在與其他學者打交道時,他極度自信且易怒。差不多他所有的著作,確實都有塔木德研究的正字標記:一定會對該領域的其他著作進行評注、批評。
馬克思成為一位古典學者,後來專攻哲學中盛行的黑格爾辯證法。他有博士學位,但他是從水準低於柏林大學的耶拿大學(Jena University)拿到學位的。他似乎始終沒有優秀到在大學謀得一職。一八四二年,他成為《萊茵新聞》(Rheinische Zeitung)的記者,並主編了五個月,直到這份刊物一八四三年被禁。其後他為《德法年鑑》(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與其他巴黎刊物寫稿,直到他一八四五年被驅逐出境。接著,是在布魯塞爾被驅逐出境。之後他參與建立共產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並於一八四八年寫出《共產黨宣言》。革命失敗後他被迫搬走(一八四九年),在倫敦落腳,之後便永久定居於此。有些年,在一八六○年代與一八七○年代,他再度投身革命的政治活動,經營國際工人協會 1,但大多數時間都窩在倫敦。他直到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世過世為止,也就是長達三十四年,都耗在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為龐大的《資本論》找資料,並試著把這些資料整理成可發表的形式。他一八六七年得以看到第一卷出版,但第二卷、第三卷是他的同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從他的筆記彙編而成,並在他死後才出版。
所以,馬克思過著學者的人生,他一度抱怨:「我是一台注定要對書籍狂吞猛嚥的機器。」[3] 但從更深的意義來看,他實在不是一個學者,也完全不是科學家。他感興趣的不是挖掘真相,而是宣揚真理。馬克思是由三個面向組成的:詩人、記者與倫理學者,每個元素都重要,組合為一體,便是他龐然怪物般的意志,讓他成為一個極難對付的作家與預言家。但他的一切都與「科學」無關。更確切地說,所有的問題就出在他反科學。
馬克思的詩人元素遠比一般所想的還重要,儘管他的詩人形象很快就被政治幻想所吞噬。他年少就開始寫詩,圍繞著兩個主題:第一個是他對鄰家女孩燕妮.威斯伐倫(Jenny von Westphalen)的愛慕,她有普魯士 — 蘇格蘭(Prussian-Scotch)血統,與他在一八四一年成婚。第二個是世界的毀滅。他寫了大量詩作,當中有三卷寄給燕妮的手稿,由他們的女兒蘿拉(Laura)繼承,並在她一九一一年過世時不知去向。不過有四十首詩的抄本留存下來,包括一齣以韻文寫成的悲劇《奧蘭尼姆》(Oulanen),馬克思認為這部作品可以成為他那個時代的《浮士德》。有兩首詩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發表於柏林的《雅典娜》(Athenaeum)雜誌,標題為「兇殘之歌」,而兇殘正是其詩作的特有調性,再加上對人類處境濃烈仇恨的悲觀主義,對腐敗與暴力、集體自殺與跟魔鬼立約的迷戀。「我們被束縛,被粉碎,被掏空,被驚嚇/永久地被拘禁在這大理石磚一般的軀殻裡,」年輕的馬克思寫道,「…… 我們是冷酷的神豢養的猩猩」。他把自己當作神,說「我將發 出怒吼,詛咒人類」,而在他大部分的詩作表面之下,包含了「整體世界危機正在擴大」的觀點。[4] 他喜歡引述歌德《浮士德》中魔鬼「梅菲斯特」的詩句「一切的存在都活該毀壞」,例如在他反對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霧月政變(The Eighteenth Brumaire)的小冊子上就那樣寫。他終其一生,對既存系統將迎來美好的、翻天覆地的結局,都抱持這種末日的異象,他的詩透露了這點,這是他在一八四八年寫出《共產黨宣言》的背景,並在寫作《資本論》時達到高潮。
總之,馬克思從頭到尾都是個末世論作家。值得注意的例子,比如《德意志意識形態》(The German Ideology)的初稿,他在一個段落熱烈緬懷過去的詩作,在涉及「審判日」之處,「天堂看見已焚毀的城市的倒影…… 而《馬賽進行曲》(Marseillaise)與《卡馬尼奧拉曲》(Carmagnole)所組成的『天國和聲』,加上轟然雷動的火砲伴奏,斷頭台行刑的時間滴答作響,熊熊火燄發出刺耳的聲音說著:會好起來的,一會好起來的。自我意識被絞死在街燈柱上 2」。[5] 然後再一次,《共產黨宣言》裡出現了模仿《奧蘭尼姆》的句子,由無產階級披上英雄的斗篷。[6] 在他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四日令人毛骨悚然的演說中,詩裡的末日調性再次爆發:「歷史即審判,其劊子手為無產階級。」恐怖的事物、房子上的紅十字標記、慘敗的象徵、地震、熔岩在地殼破裂時沸騰起來。[7] 重點是馬克思「最後審判日」的概念,無論在其恐怖的詩中異象,或其最終的經濟異象,都是藝術的概念,絕非科學。這種異象一直縈繞在馬克思心中,而身為一個政治經濟學家,他是先設立目標再去追索,為了得出「異象必然發生」的結論去尋找證據,而不是以進步的方式,客觀地檢驗資料推論結果。想當然耳,詩人的性格會讓馬克思的歷史推斷充滿戲劇性,讓激進的讀者深深著迷,因為他們想要相信資本主義的死亡與審判即將到來。馬克思的經歷明白顯示,他寫詩的天賦不時出現,產出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段落。在此理解下,他是憑直覺知道結果、而非憑理性或推論。馬克思到死都是一個詩人。
但他同時也是記者,某種程度來說,他記者做得挺出色。馬克思發現要制定計畫寫出一本大部頭的書,不光很難,是根本不可能。即便是《資本論》,也是他將一系列論文用膠水黏貼成冊,不是真正的一本書。但他非常適合寫立場鮮明、尖銳的、回應重大時事的短篇文章。他的詩人想像力告訴他,社會即將崩潰,所以幾乎每一件新的大事發生,都能與這個大原則產生關連,這給予他的新聞工作顯著的一貫性。一八五一年八月,有個早期社會主義者歐文(Robert Owen)的追隨者,即當時《紐約每日論壇報》(New York Daily Tribune)的資深主管丹納(Charles Anderson Dana),延攬馬克思成為該報歐洲政治版的通訊記者,每週要寫兩篇文章,每篇稿費一英鎊。接下來十年,馬克思貢獻了近五百篇文章,當中一百二十五篇是由恩格斯捉刀代筆。這些文章在紐約被大幅抽換與改寫,但其中最有力的論述,是純粹的馬克思風格。事實上他最大的天分是做一個製造爭議的記者,操用機智的短句與警句。許多東西都不是他的發明,「工人沒有國家」與「無產階級除了身上的枷鎖,沒什麼好失去的」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知名政論家馬拉(Marat)創造的警句。從德國詩人海涅(Heine)那裡取來的知名笑話是,有個資產階級在背部戴著封建制度時代的盾形紋章,「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句話也是。法國社會主義政治家路易.勃朗(Louis Blance)貢獻了名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而「各國的工人們,聯合起來!」則來自德國勞工領袖夏佩爾(Karl Schapper)。但馬克思有能力自己創造,比如「在政治上,德意志對其他國家的做法已有主見」、「宗教只是人類開始自轉以前,繞著打轉的假恆星」、「資產階級的婚姻是妻子共有制」、「革命敢於向對手叫罵最挑釁的字眼:我很渺小,但我一定最重要」、「每個年代的統治觀念,都是其統治階層的觀念」。此外他具備罕見的天分,能凸顯他人的格言,並在自己的論點中,以正確的位置、致命的組合,精準地運用這些元素。沒有政治作家能超越他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後三句話:「無產階級除了身上的枷鎖,沒什麼好失去的。他們將獲得全世界。全世界的工人,聯合起來!」馬克思運用記者的眼光,發現比起任何事物,短而精煉的句子更能避免他完整的哲學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被遺忘。
如果詩提供了異象,而記者的警句使馬克思的作品出眾,則使之穩重的,是學術的專門術語。馬克思是學者,更確切地說,是一個不及格的學者。滿腔憤怒、本來想做大學研究員的人,打算以新的哲學流派震撼全世界──這同時也是他謀取權力的計畫。因此,他對黑格爾的態度矛盾,他在德文第二版《資本論》的序言中寫道,「我承認自己是這位偉大思想家的信徒」,以及「我在討論《資本論》的理論價值時,耍了耍黑格爾的專門術語」。但他說他的「辯證法」與黑格爾的恰好相反,對黑格爾來說,思考程序是創造了現實,可是,「另一方面,在我看來,觀念不過是在人類大腦裡被調換與轉化的現實物質而已」。因此他主張,「在黑格爾的著作裡,辯證法顛倒了實際的順序。如果你想要找到包藏在騙人把戲裡的合理核心,你得再次把它導正」。[8]
於是,馬克思用他對黑格爾方法中發現的致命缺陷,來追求學術聲望,企圖以全新的哲學取代整個黑格爾體系,更確切地說,那是一種讓所有既存哲學都變得過時的超級哲學。但是他繼續相信黑格爾的辯證法是「理解人類的關鍵」,不但繼續使用,還至死都是它的囚徒。因為辯證法及其「矛盾論述」解釋了不斷升溫的全體危機,而這個危機源自於他十多歲就懷抱的詩人異象。他在即將到達生命終點時(一八七三年一月十四日)寫到,景氣循環顯露出「資本主義社會內在固有的自相矛盾」,並將生成「這些循環的最高點,一場全體的危機」。這會導致即便是「新德意志帝國的暴發戶」也會「反覆講述辯證法」。
這跟現實世界的政治與經濟有任何關係嗎?什麼也沒有。就像馬克思的哲學原本的出發點就是一個詩人異象,所以其精緻美妙的闡述,也只是把異象操作成難懂的術語。然而,要讓馬克思的智識手段開始運作,需要道德上的推動力。他在對高利貸者與放款者的敵意中找到了這種激情,與他的財務困難直接相關(後文會說到)。馬克思早期的系列作品中可以看見這種情緒,例如有兩篇題為《論猶太人問題》(On Jewish Questions)的論說文,在一八四四年的《德法年鑑》上發表。黑格爾的追隨者全都反猶太人,只是程度不一,在一八四三年,黑格爾左派留下的反猶太領袖鮑威爾(Bruno Bauer)發表了一篇論述,要求猶太人全面禁止猶太教。馬克思的論說文是回應此篇文章,他不反對鮑威爾的反猶太主義。更確切地說,他自己也分享這篇文章,予以認同,且引述以表贊同。但他不同意鮑威爾的解決方案。鮑威爾認為猶太人反社會的根源是宗教,只要撕裂猶太人的信仰,就能夠矯正;馬克思則否決了鮑威爾的看法,在他的觀點裡,猶太人的罪行是在社會與經濟層面。他寫道:「讓我們想想真正的猶太人。不是安息日的猶太人,而是日常的猶太人。」他問:「猶太文明的世俗基礎是什麼?一定有務實、利己。猶太人的世俗狂熱是什麼?做小商販。他們的世俗信仰是什麼?錢財。」於是,猶太人漸漸地把這種「務實的宗教」傳揚到整個社會:
錢財是以色列小心守護的神,若沒有錢財,其他的神都不會存在。錢財讓人類其他神祇的地位都矮了一截,並把祂們都變成了有價之物。錢財用自己的價值衡量所有物品。所以,錢財奪走了整個世界自身真實的價值,包括人類世界與大自然。錢財是讓人類的工作及存在異化的要素:該要素支配了人類本身,而人類敬拜它。猶太人的神一直都在世俗化,而且已經成了世界之神。
猶太人使基督徒墮落,並說服他們「除了變得比鄰人更有錢,沒有其他使命」,而且「這世界是一間交易所」,政權成了金權的「奴隸」。因此,解決方案要著眼於經濟。金錢活動有「極高的可能性」招致這種問題,「金錢 — 猶太人」成了「當前眾所周知的反社會要素」,使得「猶太人令人生厭」,所以必須徹底破壞那個「先決條件」。要廢除猶太人對錢的態度,同時也得廢除猶太人及其宗教,則猶太人在這世界腐化基督教信仰的異象就會消失:「把自己從金錢跟生意行為中解放出來,也就是從務實的猶太文明中解放出來,我們的時代將會自我解放。」[9]
如此這般,馬克思對世界的錯誤解釋,彷彿是學生餐廳裡的反猶太主義與盧梭思想的組合。接下來三年,從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四六年,他將之擴充成他的成熟哲學。在此期間,他決定了社會的有害要素、必須推翻的高利貸金權,不光只有猶太人,還包括全部的資產階級。[10] 為達此目的,他煞費苦心地利用黑格爾的辯證法──這一頭有金權、財富、資本,是資產階級的工具,另一頭有新的救贖力量:無產階級。他以嚴謹的黑格爾表述法提出論據,使出所有能想得到的德國哲學術語,儘管他的動力顯然是道德與最終異象(末日危機),而這依然是詩性的。因此,革命即將到來,在德國,那將是一場哲學革命。「單一社會階層無法自我解放,除非它解放了所有社會階層。簡言之,人類單靠贖罪的自我解救能力,已經完全喪失。這種分崩離析的社會,以一個特殊階層稱呼它,即是無產階級。」馬克思似乎是要說,無產階級是一種不屬於階級的階級,能溶解所有階級,是一種從來沒有被記載的救贖力量,不會臣服於歷史法則,而且終將在歷史之中終結歷史──很詭異,這是一個非常猶太人的概念,無產階級將成為彌賽亞或救世主。此革命包括兩個要素:「解放的腦袋是哲學,心臟是無產階級。」如此一來,知識分子將來自社會精英、一般大眾、工人與步兵。
把富人階層的範圍從猶太金權擴張到整個資產階級,再用新的哲學來界定無產階級之後,馬克思繼續在他哲學的核心運用黑格爾辯證法,為這場大危機設下大事件。這段關鍵的段落如此作結:
無產階級將正式宣吿私有財產歸其所有,就像他們也宣吿雇傭勞動(Wage-labour)是替別人產生財富,為自己製造窮苦。如果無產階級勝利了,那完全不是為了成為社會的專制者,而只是為了廢除自身階級及其對立面。然後無產階級及其注定的對立面,私有財產制,將會消失。
馬克思就這樣成功界定了他在詩人異象所見到的大災變,不過這個定義是用德文術語寫成,從大學殿堂以外的現實世界來看完全不知所云。
即便馬克思將這些事件政治化,但他仍是使用哲學術語:「沒有革命,社會主義無法成立。當有組織的行動展開,當靈魂、事物的內在開始顯現,則社會主義就能揭開所有政治的面紗。」馬克思是一個真正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他和維多利亞女王寫信的時候也一樣,經常在文句下畫線強調,但他的強調,實際上並未在傳達意思上幫上太多忙,其含義依舊沉沒在德文的、學術的、哲學用語的晦澀概念之中。為了讓世人接受,馬克思也求助於典型的誇大敘述,強調他描述的是全球性的過程,卻同樣被術語拖累。例如他說:「無產階級只能在世界史的觀點中存在,就像共產主義一樣,其行動也只能在世界史的觀點中存在。」或是:「在經驗上,共產主義是統治階層全體、立即、同時行動才可能存在,其前提是全面發展的生產力及仰賴生產力的世界貿易。」不過,即便馬克思的意思很清楚,他的陳述也未必有效,而只是一個道德哲學家不具約束力的附帶意見。[11] 以上我引述的部分句子,如果改成是相反立場的話,聽起來也同樣似非而是或似是而非。所以,這位道德哲學家,是如何把這些先知性言論、把這些天啟,變成真實世界的事實證據與科學的呢?
馬克思對事實的態度矛盾,一如他對待黑格爾的哲學。一方面,他花了好幾十年收集事實根據,共累積了上百本龐大的筆記,但這些在圖書館發現的事實,是官方事實。藉由那些居住在世界之中的人民,透過親眼親耳檢驗所發現的事實,不是馬克思會感興趣的事實。他是個徹底、無藥可救的書呆子,世上沒有任何事物能把他趕出圖書館。他對貧窮與剝削的關注要追溯到一八四二年秋季,當時他二十四歲,正在寫一系列的文章,探討在地農夫採集木材之權利的管理法規。根據恩格斯的說法,馬克思告訴他,「他所研究的法規涉及竊木問題,而他對萊茵河的支流摩澤爾河(Moselle)農民行為的調查,使他的注意力從單純的政治轉至經濟情況,再轉向社會主義」。[12] 但沒有證據顯示馬克思曾經跟這裡的農民與地主實際講過話,或是親自訪視現場。此外,一八四四年他為《前進報》(Vorwärts)寫金融週報,有一篇是探討中歐西利西亞(Silesia)織布工的困境。但他從沒去過西利西亞,或者,就我們目前所知,沒有跟織布工談話的任何記述,如果有,那也非常不像他會做的事。馬克思一生都在寫關於金融與製造業的文章,但他認識的人當中,只有兩位跟金融或製造業流程有關,一位是他在荷蘭的姨丈利奧.菲利普(LionPhilips)。菲利普是成功的商人,最終創立了龐大的飛利浦電子公司(PhilipsElectricCompany),而他對於處理資本主義的看法,肯定見識廣博且饒富趣味,讓馬克思在探究時遇上麻煩。但馬克思只有在談到高級財務學的技術問題時,向他請益過一次,而且儘管曾經四度拜訪,馬克思關切的也只有家族資金的私人問題。另一位博學的人是恩格斯本人,他曾經邀請馬克思去參訪棉花工廠,但被婉拒了。就我們目前所知,馬克思終其一生,都從未親自踏足任何一間磨坊、工廠、礦井或其他製造業的工作場所。
更令人訝異的是,馬克思敵視有這類經驗的革命夥伴──也就是開始有政治意識的工人。他一直到一八四五年才與這些人接觸,當時他短暫造訪倫敦,參加當地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German Workers’ Education Society)的會議。他對所見所聞感到不悅,這些人大多是有專門技術的工人、鐘錶匠、印刷工、製鞋工人。他們的領導人是林務人員。他們自學、受過訓練、嚴肅、舉止有禮,非常反對放蕩不羈的藝文圈,急著改變社會,但是對達成目標的實際措施態度謹慎。他們沒有馬克思的天啟異象,最重要的是,他們不使用他的學術術語。馬克思藐視他們:他們當不成革命的先鋒。馬克思總是偏愛像自己一樣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他與恩格斯創立共產主義者同盟時,以及成立第一國際時,都設法將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者從任何有影響力的位置上排除,而只是以無產階級的名義坐在委員會席上。他的動機有部分是因為知識分子的勢利眼,部分是因為真正有工廠實務經驗的人,傾向於反對暴力,偏愛穩定、漸進的改善:那些人有足夠的見地懷疑他所宣稱的天啟式革命,其中的必要性與必然性。馬克思有一些最惡毒的譴責,是直接用在這些人身上。例如在一八四六年三月,他在一場「考驗」中試圖讓威廉.魏特林(Willian Weitling)屈服,時間就在共產主義者同盟於布魯塞爾舉行會議之前。魏特林很窮,是一個洗衣女的私生子,始終不知其父姓名,他在裁縫店當學徒,十分賣力地工作與自學,為自己贏得了大批的德國工人追隨者。「考驗」的目標是堅定主義的「正確性」,貶抑任何高傲的工人階級,這類人缺乏馬克思的思想所必要的哲學訓練。馬克思對魏特林的攻擊極其猛烈,馬克思說,他有罪,因為他在指揮一場運動時沒有中心主義。這種行為在未開化的俄羅斯沒什麼,在那裡「你可以用愚蠢的年輕人和使徒,建立成功的聯合會。但在文明國家,像是德國,你就得理解,沒有主義,什麼都辦不到」。還有:「如果你企圖影響工人,特別是德國的工人,沒有主義與清楚的科學觀念作為軀幹,那你就只是在玩一場空洞又不道德的傳教遊戲,將無可避免地造出一位受了啟發的使徒,讓聽他們講道的蠢驢們目瞪口呆。」魏特林回應,他不是一個在研究中編造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他為真正的工人發聲,不會屈從於那些「跟這苦難世界裡真正勞工相隔甚遠」的純理論家。有位目擊者說:「這使馬克思勃然大怒,他用拳頭奮力捶桌子,捶到桌燈都搖晃了。他跳腳大吼『無知從來就沒幫上任何人』。直到會議結束,馬克思都還在暴怒,在房間裡到處跺腳。」[13]
這是馬克思對工人階級出身的社會主義者,以及任何被大批的工人追隨的領袖,進一步的攻擊模式,因為他們鼓吹的是對工作與薪資實質問題的務實解決方案,而不是空有教條的革命。例如,馬克思攻擊當過排字工人的法國經濟學家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農業改革者克里基(Hermann Kriege),以及首位擁有實權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士暨勞工組織者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馬克思對農業一竅不通,尤其不了解克里基落腳的美利堅合眾國,但他在《反克里基宣言》(Manifesto Against Kriege)裡,譴責克里基提議給予每位農民一百六十英畝的公地。他認為應該用承諾的土地招募農民,可是一旦共產社會建立起來,土地就得變成共同持有。普魯東反對教條主義,他寫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在我們終於推翻所有(宗教的)教條主義後,別再讓企圖灌輸人民另一種教條的任何事物滲透進來了…… 別再自己製造新的、不寬容的領袖了。」馬克思痛恨這幾句話。他在一八四六年六月所寫的《哲學的貧困》(Misèredela Philosophie)中,長篇大論地抨擊普魯東,指控他是「幼稚鬼」,對經濟學與哲學「非常無知」,尤其誤用了黑格爾的概念與技巧──「普魯東先生對黑格爾辯證法的理解僅止於其慣用語。」至於拉薩爾,則成了馬克思反猶太與種族歧視情結中最殘酷的受害者:他是「猶太鬼爵士」、「猶太胚子」、「掩藏在美髮油與廉價首飾之下的猶太滑頭」。「如今我清楚得很」,馬克思在一八六二年七月三十日寫給恩格斯的信中說,「他的頭型和頭髮顯示,他是和摩西一起逃出埃及的黑人後裔(除非其母或父親那一系的祖母曾與黑人雜交)。這種猶太與德意志在黑人基礎上的結合,一定會製造出異常的雜種」。[14]
當時,馬克思既不願意親自調查製造業的工作條件,也不願意向聰明又有親身經歷的工人學習。他何需這麼做呢?運用黑格爾的辯證法──即在所有必要條件裡,他已經在一八四○年代末得出人類命運的結論,剩下的就只有找出事實來證明它們。這些事實能從新聞報導、政府藍皮書(官方報告),以及前輩作家們所搜集的證據中獲得;而且所有資料都能在圖書館裡找到。那何必再看得更遠?要解決的就像馬克思所看見的那樣,是找到類型正確的事實:相符的事實。哲學家亞斯培(Karl Jaspers)相當貼切地總結了他的方法:
馬克思的寫作風格不是研究人員那種…… 若是違反他的理論,他不引述例子,也不列舉事實,只引述那些明顯能支持或確立他所認為的終極真理者。其方法只是為了替自己辯護,不是研究調查。然而,為某事辯護之後宣吿這是有根據的十足真理,這不是科學家,而是信徒。[15]
在此理解下,「事實依據」不是馬克思的核心工作;它們是附屬的,用以支撐早已得出的不相干結論。因此,他畢生學問的不朽經典《資本論》,不可視為他所聲稱的「對經濟進程之特質的科學調查結果」,而是一種道德哲學的運用,堪與維多利雅時代的評論家卡萊爾(Carlyle)與拉斯金(Ruskin)相提並論。《資本論》的篇幅驚人,而且經常出現前後不一的冗長說教,攻擊製造業的流程與所有權的原則,表達出一個強力,但本質不理性的憎恨。說來也怪,這本書沒有一個核心論點來整合內容,馬克思在一八五七年時,原本打算將這部作品寫成六卷:資本、土地、薪資與勞工、政府、貿易,以及最後一卷,論世界市場與危機。[16] 但要完成上述計畫,需要有條不紊的自我約束,事後證實這超出他的能力。他實際產出的唯一一卷(令人困惑的是,現在成了兩卷)毫無邏輯模式可循,是一系列隨意安排先後順序的個人解說。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圖塞(Luis Althusser)發現其架構是如此令人困惑,以至於必須要求讀者略過第一篇,直接從第二篇,也就是第四章開始讀,[17] 但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評注者憤怒地駁斥這種見解。事實上,阿圖塞的方法也沒太大幫助。恩格斯寫的《資本論》第一卷一覽表,只強調出薄弱之處,沒指出結構上的缺失。[18] 馬克思死後,恩格斯從馬克思一千五百頁對開本的筆記中,製作出第二卷,改寫了其中的四分之一,結果用了枯燥凌亂的六百頁來談論資本的流通,大部分是探討一八六○年代的各種經濟理論。恩格斯從一八八五年工作到一八九三年的第三卷,全面考察資本尚未涵蓋的所有面向,但也不過是一系列的注釋,包括用一千頁來討論高利貸,內容大多是馬克思的備忘錄。這些龐大資料注記的日期幾乎都是一八六○年代早期,同一時間馬克思也在寫第一卷。事實上,沒有人可以阻止馬克思完成這部作品,除了他自己。他精力不足,而且不知道一切雜亂無章。
第二與第三卷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因為馬克思不太可能希望它們以這種形式面世,這兩卷的工作實際上已經停擺十五年。在第一卷(他的作品)中,真正重要的只有兩章,第八章《工作日》與即將進入第二卷的第二十四章《原始積累》,其中包括知名的第七節「資本積累的歷史傾向」。上述內容不管怎麼理解都不是科學分析,而完全是預言書,馬克思說未來會「一、資本巨頭的數量將逐漸降低。二、相應地,會增加大量的貧窮、壓迫、奴役、衰退與剝削。三、工人階級穩定地加劇其憤怒的行為」。這三股力量一起發作,將產生黑格爾哲學的危機,或是他所謂的政治經濟異象,就像他年少時那些如詩般的大災變想像:「這些生產工具的集中化,與勞工的社會主義化,到達一個只剩資本主義軀殼、實際上互不相容的程度,這將會爆炸成碎片。資本主義者私有財產制的喪鐘敲響了,剝奪者們將反被奪走一切。」[19] 這聽起來非常令人興奮,讓許多世代的社會主義狂熱者相當鼓舞,但其預言內容在科學上,並沒有比一本占星年鑑還強。
相較之下,第八章《工作日》描述資本主義對英國無產階級生活的影響,確實提出了有事實根據的分析,更確切地說,這是馬克思的作品中唯一真正處理到勞工的部分,是他整個哲學在表面上的主題,因此值得檢驗一下它的「科學」價值。[20] 由於我們已經注意到,馬克思只找符合自己成見的事實,這背離所有科學方法的原則,使得這章從一開始就有根本的弱點。但馬克思除了根據偏見選擇事實,是否還會歪曲或竄改事實?我們必須思考這一點。
該章試圖主張的論點,以及馬克思道德理論的核心,即在於資本主義的本質必然會對工人漸進地加重剝削。也因此,越多的資本用於雇用勞工,就有越多的勞工被剝削,這是極大的道德罪惡,會製造最後的危機。要證實這個論點的科學正當性,馬克思必須證明:一、前資本主義時期(pre-capitalist)的小工廠工作條件就很惡劣了,但在工業資本主義(industrial capitalism)之下還會更加惡化。二、假定資本的本質無情且難以改變,在資本化達到最高的產業中,對工人的剝削會增強到最高點。關於第一點,馬克思連嘗試都沒有,他寫道:「就英格蘭有大規模製造業開始到一八四五年這段期間,我應該只是略為提及,詳情請見恩格斯《英格蘭工人階級的工作條件》(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馬克思補充說,後來的政府出版品,尤其是工廠視 察員的報告,已證實「恩格斯洞見了資本主義者手段的本質」,以及「他所描述的環境,對細節的存真值得讚揚」。[21]
簡言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篇中所有對一八六○年代中期工作條件的科學檢驗,主要基礎都來自一部作品,就是恩格斯二十年前出版的《英格蘭工人階級的工作條件》。因此相對地,馬克思研究的科學價值,是否也可以依據這項單一資料來源呢?恩格斯出生於一八二○年,是萊茵地(Rhineland)巴門城(Barmen)一家殷實的棉花製造商之子,他在一八三七年進入家族企業任職。一八四二年,他被派往公司的曼徹斯特辦公室,在英格蘭待了二十個月,在此期間他造訪倫敦、奧海姆(Oldham)、洛奇代爾(Rochdale)、阿什頓(Ashton)、利茲(Leeds)、布拉德福(Bradford)、哈德斯菲爾德(Huddersfield)等地,當然也包括曼徹斯特,因此他對紡織原料的貿易有直接經驗,但除此之外,對英國的情況並未握有第一手的資訊。例如他對礦業一無所知,也從沒下過礦坑;他也不知道鄉下地區或農村的勞動情形,但他還是寫了整整兩章的《礦工》(The Miners)與《田地上的無產階級》(The Proletariat on the Land)。一九五八年,兩位真正的學者,美國歷史學家韓德遜(W.O.Henderson)與查洛納(W.H.Challoner),在翻譯與編輯恩格斯的著作時,查核了他所有資料來源跟引文出處,[22] 結果幾乎是毀了全書的客觀歷史價值,使得此書評價再無可疑:該書是一部有關政爭的著作,一份文宣,以及一篇長篇的攻擊性演說。恩格斯在寫作時,致信給馬克思說:「在這場關於世界輿論的法庭裡,我指控英國中產階級犯了大規模的屠殺、搶劫和法條裡的所有罪行。」[23]
這番話恰恰總結了這本書:寫這本書就是為了控訴。其中諸多內容,包括對前資本主義時期與工業化早期階段的考察,都不是根據原始的資料來源,而是許多價值可疑的二手來源,特別是蓋斯凱爾(Peter Gaskell)一八三三年的《英格蘭的製造業人口》(The Manufacturing Population of England),這是一部浪漫時代的神話,企圖證實十八世紀是英國自由民與工匠的黃金時代。事實上,正如一八四二年皇家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對童工的調查,最終證實小型的、前資本主義的作坊與村舍裡的工作環境,比蘭開郡(Lancashire)的棉花工廠惡劣多了。恩格斯援引的原始資料已經是在五、十、二十、二十五,甚至四十年前的出版物,儘管他引用了這些「同時代」的資料,他給的夜班工人非婚生嬰兒的數據,也刻意不提源自一八○一年,而他引述了一份愛丁堡環境衛生的報告,卻沒說該報告寫於一八一八年──他屢次刻意不提他的事實與證據早已因為過期而完全失效。
恩格斯的不實陳述是蓄意要欺騙讀者還是他自己,始終都不是很清楚。但有時這種欺騙顯然是刻意的,他用了工廠調查委員會在一八三三年顯示工作環境惡劣、有害健康的證據,卻未告訴讀者一八三三年英國財政大臣奧爾索普子爵(Lord Althorp)便已批准《工廠法》(Factory Act),而且實施已久,大幅減少了報告中描述的情形。他在處理其中一個主要參考資料,凱|沙圖華茲博士(Dr. J.P.Kay)的《曼徹斯特棉花工廠受雇的工人階級,其客觀與道德條件》(Physical and Moral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Employed in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Manchester)時,使用相同的詭計。沙圖華茲博士的著作協助推動了當地公共衛生設施的重大改革,但恩格斯沒提到這些,他誤解犯罪率的統計數字,或是在無法支持他的立場時忽視它們。更確切地說,他時常故意隱瞞否定其論點的事實,或是阻止他所嘗試揭發的「特殊罪惡」的事實。細看恩格斯從二手資料中引述的內容,經常都被刪節、縮減、斷章取義或是曲解,唯一不變的是會加上引號,看起來彷彿是逐字逐句引述。《英格蘭工人階級的工作條件》的韓德遜與查洛納英譯版本,從頭到尾都是記載恩格斯歪曲事實與欺騙的注腳,單單第七章《無產階級》,謊言與謬誤,包括事實的錯誤竄改,就出現在第一五二、一五五、一五七、一五九、一六○、一六三、一六五、一六七、一六八、一七○、一七二、一七四、一七八、一七九、一八二、一八五、一八六、一八八、一八九、一九○、一九一、一九四頁,與二○三頁。[24]
馬克思不可能沒察覺恩格斯著作中這些確實的缺失與欺瞞,因為早在一八四八年,早已被德國經濟學家希爾德布蘭(Bruno Hildebrand)揭發,馬克思對該書熟悉得很。[25] 此外,馬克思自己也使用恩格斯歪曲事實的陳述法,故意不告訴讀者在這本書出版之後,由於《工廠法》及其他改善法規之實施,勞動條件已大幅改善,而影響的恰恰是他所
強調的勞動條件類型。無論如何,馬克思運用第一手或第二手的資料來源,都是以相同精神:十足隨便、心懷偏見地扭曲事實,以及他對恩格斯的作品那種完全不公正的評價。[26] 他們確實常常一起騙人,但馬克思是更厚顏無恥的偽造者。有個案例特別明目張膽,他甚至在此超越了自己。他對成立於一八六四年九月的第一國際,發表所謂的「就職演說」(Inaugural Address)。為了煽動漠不關心的英國工人階級,讓他們焦慮,證明生活水準正在下降,他蓄意竄改英國首相威廉.格萊斯頓(W. E. Gladstone)在一八六三年財政預算演講時的一個句子。格萊斯頓在評論國民財富增加時,說的是:「我應該幾乎是戒慎恐懼地看著財富與權力令人興奮的增長,照我看法的話,增長只存在於生活富裕的階級。」但他補充:「我們也樂於知道,英國勞工的平均條件在過去二十年,已經改善到令人意想不到的程度,改善到我們幾乎可以宣布,這在任何國家、任何年代,都是前所未見的。」[27] 馬克思在他的演講中描述格萊斯頓的話:「財富與權力令人興奮的增長,只限於資產階級。」格萊斯頓是這麼說沒錯,但他有大量的統計數據加以佐證,而且無論如何他都知道必須念茲在茲,確保財富盡可能分配得越廣越好,很難想像有人把他的意思顛倒得如此無恥。馬克思將它當成原始資料提供給《晨星報》(Morning Star),但《晨星報》與其他報紙,以及《英國國會議事錄》(Hansard),都校正了對格萊斯頓演說的引述。馬克思的引用錯誤被指出來,但他還是在《資本論》中複寫一遍。此外還有其他的不一致,而當他的竄改又再次被注意、告發,他表示墨水溢出而造成了混淆。他、恩格斯,以及後來他的女兒愛琳娜(Eleanor)都串通一氣,為這站不住腳的事件辯護了二十年。他們沒有一個人承認這些明目張膽的竄改,而爭辯的結果讓部分讀者誤會了這件事,就像馬克思所盼望的,兩邊的人馬加入公開論戰。但是,馬克思其實知道格萊斯頓沒說過那種話,他的欺騙是蓄意而為。[28] 這並非單一個案。馬克思在引述時,也同樣竄改了亞當.斯密的話。[29]
馬克思有系統地誤用資料來源,在一八八○年代吸引了兩位劍橋學者的注意。他們藉由《資本論》的法文修訂版(出版於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五年),一八八五年在劍橋經濟俱樂部(Cambridge Economic Club)出版了一份報告,叫做「對卡爾.馬克思於《資本論》第十五章運用藍皮書之意見」。[30] 他們說第一次檢查馬克思的參考文獻時,「是為了取得某些地方更完整的資訊」,但是礙於「不相符之處持續增加」,於是決定仔細檢查「明確錯誤的範圍與嚴重性」。他們發現政府藍皮書的文本,與馬克思的引述有所出入,而且不是單一的錯誤,「有著曲解事實的影響力」。在某些狀況下,他們發現引述的話經常「視情形縮短,省略了許多可能違反馬克思亟欲建立之結論的段落」。另一種是「從報告的不同篇章,把許多片段組合在一起,偽裝成一個單獨的聲明,加以引述。然後強迫讀者接受,好似引號內容全是從藍皮書直接引述的當局說法」。比如在講縫紉機的主題上,「他肆無忌憚地使用藍皮書,極為惡劣…… 就為了證明其所建立的、與現實相反的論點」。這兩位學者推論:找到的證據可能不夠「充分到可以指控他蓄意竄改」,但肯定顯示出「在引述權威上,近乎犯罪的輕率」,並警告「看待馬克思作品的其他篇章時,必須有所懷疑」。[31]
真相是,即便是用最低的標準調查馬克思運用的證據,都會讓人懷疑他所寫的每一件事。他一直都不可信,《資本論》第八章全部的重點,就是蓄意且有系統地竄改,就一個命題的論證而言,他的論據在客觀檢驗時顯然站不住腳。他違背真實的罪行,有以下四條。第一,由於最新的資料不支持他的論據,所以他用過時的資料;第二,他選擇工作條件特別惡劣的產業,來作為資本主義的典型代表,這項欺騙對馬克思來說尤其重要,因為不這麼騙人,他真的也不必寫第八章了。他的命題是資本主義製造了更加惡劣的工作條件。資本家為了確保足夠的報酬,只要雇用越多人,就有越多工人受到惡劣待遇。但他所引述的證據,最終證實了幾乎全都是過時產業裡規模最小、最無效率、投資不足的企業,多數個案屬於前資本主義時期,例如陶器廠、女裝裁縫、鐵匠、烘焙、火柴、壁紙、蕾絲等。在許多他所提出的特定案例中(像是烘焙),工作條件確實惡劣,因為公司缺乏資本,負擔不起引進機器的費用。實際上,馬克思處理的是前資本主義時期的工作條件,而無視於擺在他面前的事實──資本越多,受苦越少。他確實探討了現代的、高度資本化的產業,像是鋼鐵業,但他發現缺乏證據,於是利用經過竄改的批評(例如:多麼諷刺!/這只是在硬拗!)。至於鐵路公司,他則不得不拿出古早意外事故的聳動新聞片段(例如:最新鐵路災難),他的命題需要乘客在每一公里的事故發生率都提高才行,但是實際數字反而急遽下降,在《資本論》出版時,鐵路已成為世界史上大眾運輸最安全的模式了。
第三,當馬克思引述工廠稽查員的報告,指出勞工惡劣的工作條件與不友善的待遇,並將之視為體制上無法避免的情況時,實際上,那些稽查人員口中「哄騙的工廠老闆」已經被指出、看穿且起訴了,受害人數在此過程中不斷減少。第四,馬克思以視察人員的報告作為資料來源,這揭露了他最大的謊言。他主張資本主義的本質無可救藥,更進一步來說,資產階級政府將帶給工人窮困與不幸,正如他所寫:「政府,是整個管理階級為了控管而設置的執行委員會。」但真如此的話,國會怎麼會通過《工廠法》,政府也不會執行這項法案了。差不多所有馬克思的事實,都是選擇性地利用(有時是竄改)政府(如稽查員、法院、太平紳士 3)改善工作條件的努力,而這必然會涉及揭發與懲罰這些該負責任的壞老闆。如果制度本身沒有革新──這在馬克思的理論中是不可能的──他也不會寫出《資本論》了。他不願意做任何現場調查,便不得不仰賴這些被他稱為「統治階級」的人所找出來的證據,而這些人正在努力撥亂反正,也不斷成功達到目標,於是馬克思必須選擇曲解這些主要證據,或是放棄他的命題。這本書過去是、現在也是結構性地欺騙。
由於馬克思沒有花半點工夫理解製造業如何運作,所以他無法或不願意理解一個事實,即打從工業革命在一七六○至九○年的萌芽之際,最有效率的製造業者,已經習慣大量運用資本,提供勞動者更好的工作條件,所以他們傾向於支持工廠法規。同樣重要的是,他們支持法規落實,因為這減少了他們所認為的不公平競爭。工作條件因此改善,也由於工作條件改善,工人沒有像馬克思所預測的群起反抗。這位先知於是不知所措。《資本論》暴露的問題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理解,犯了根本性的錯誤,他的錯誤正好是因為他的不科學:他不親自調查事實,或至少運用他人調查的客觀事實。不光是《資本論》,而是他的全部作品,從頭到尾都表現出對真相的屏棄,有時次數多到像是在藐視真相。這就是為何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社會體制,無法產生其所宣稱的成果。說它「符合科學」,太荒謬了。
儘管馬克思表面上是個學者,但如果他的著作動機不是對真理的愛,那麼在他的生活中,是什麼給予他激勵?為了挖掘這一點,我們必須更仔細地審視他的個人特質。以下的事實,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個可悲的事實:知識分子們大量的著作,不是出於大腦與想像力的抽象工作,而是出自深植內在的本性。馬克思是此一規律的絕佳範例,我們已經仔細談過他所提出的哲學,是他詩人異象、記者寫作技巧與學術風格的混合物。但馬克思哲學的實際內涵,也能顯示他性格的四個面向:他對暴力的喜好,他的權力欲望,他對金錢的無能,以及最重要的,他傾向利用周遭的一切。
馬克思主義裡,一直都有暴力的潛在傾向,並透過馬克思主義者統治的實際行為,不斷地顯現出來,這種統治方式是設計者本人的投射。馬克思一生都活在極端的語言暴力中,一再體驗暴力口角和人身攻擊。馬克思的家庭吵鬧不休,幾乎是他未來妻子燕妮注意到他的第一件事。在波昂大學時,警察因他持有手槍而逮捕他,他差一點就被判入獄。大學的檔案保管處顯示,他涉及學生鬥毆,與人決鬥被刺傷了左眼。他跟家人的口角讓他父親幾年來都鬱鬱寡歡,最終導致馬克思與母親徹底鬧翻。在燕妮現存最早的信件裡可以讀到這樣的句子:「請不要用這麼多的仇恨與惱怒寫信。」顯然他持續不斷的爭吵,使他寫作時使用暴力的表述方式(說話時更甚),而且往往會因酒精而加劇。馬克思沒有酒精中毒,但他定期喝酒,經常喝得太多,偶爾會參與令人擔心的拚酒較量。馬克思的個人生活有一種麻煩,他從二十幾歲開始就離開德國,住在異國城市的社會裡,只差沒放棄國籍了。他鮮少出城找朋友,也不想試著融入群體,此外,他和一起移居外國的人往來密切,其本身就是一個狹小的圈子,唯一的興趣就是革命的政治活動。這更解釋了馬克思為什麼對人生的目光狹隘,很難找到其他更能助長他愛爭吵的本性的社會背景了,這些小圈子以其兇猛而惡名昭彰。根據燕妮的說法,在布魯塞爾,這些爭吵沒有停過,而在巴黎,他在綠磨坊街 4 所舉行的編輯會議必須關緊窗戶,以免外面的人聽見無止盡的大呼小叫。
不過,這些爭吵並非漫無目標。從鮑威爾以來,馬克思跟每一個往來的人爭吵,直到成功控制了對方。結果有許多不懷好意的敘述,是馬克思狂怒之下的手筆,鮑威爾的兄弟甚至寫了一首有關他的詩:「在暴烈的痛苦中,邪惡從特里爾一路相隨/沒完沒了地吼叫,他緊握罪惡之拳/好似有一萬個惡魔,鑽進頭髮裡占據了他。」[32] 馬克思矮小、口音很重、黑髮且蓄鬍,肌膚蠟黃(他的孩子叫他「摩爾人」5),戴著普魯士風格的單片眼鏡。俄羅斯文學家安納科夫(Pavel Annenkov)目睹他對魏特林的「考驗」,形容他「有濃密的黑髮,毛茸茸的雙手,禮服大衣扣得歪七扭八」。他舉止無禮,「自負,有點瞧不起人」。他「尖銳、金屬般的聲音很適合他一直在傳達的、對人對事的激進意見」。他「以刺耳的聲調」說每一件事。[33] 他最喜歡的莎士比亞作品是《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Troilus and Cressida),他喜歡其中埃賈克斯(Ajax)與忒西忒斯(Thersites)的激烈辱罵。他喜歡引述上面那一段,有一篇文章名為「愚鈍的閣下:您腦袋裡的料,比我手肘裡的還少」,受害者是追隨他革命的海因岑(Karl Heinzen)。海因岑的報復是把馬克思描寫成一個憤怒的矮男人。他發現馬克思「令人難以忍受的髒」,是「貓跟黑猩猩的雜種」,有著「一頭凌亂的黑髮,髒兮兮的泛黃膚色」。他說,馬克思的衣服與膚色分不出天然的土色或是髒。以及那雙好鬥、惡意的小眼睛,「噴發出邪惡的火光」。還有一句口頭禪:「我會殲滅你。」[34]
馬克思大部分時間,其實都花在搜集政治對手與敵人的檔案,他並不顧忌把這些交給警方,如果這樣能在他需要時產生作用的話。那些重大的公開爭論,確實偶爾會濺血,例如一八七二年在荷蘭的行政中心海牙(Hague)舉辦的第一國際會議,就預示了蘇聯大清算的樣貌。在史達林主義者的時代,沒有任何事物不令人想起馬克思的行為。馬克思在一八五○年與魏理希(August von Willich)的爭吵中便是這麼惡語毀謗,以至於後者向他要求決鬥。馬克思雖然之前跟人決鬥過,這次卻表示「不願投入普魯士軍官的遊戲」,並無意阻止他的年輕助手施拉姆(Konrad Schramm)替他上場。但施拉姆從未用過手槍,而魏理希精於射擊。施拉姆中槍受傷了。魏理希的第二槍,是射向一位跟馬克思有關係的狡猾之人,鐵肖(Gustav Techow)。燕妮有理由厭惡他,因為他殺了至少一名革命追隨者,最終因為謀殺警察被判處絞刑。當跟自己的策略合拍時,馬克思就不排斥暴力、甚至恐怖主義,一八四九年在談到普魯士政府時,他威脅:「我們殘忍無情,不會向你們求情討饒。當輪到我們占上風時,我們必不會掩飾我們的恐怖手段。」[35] 隔年,他以德文書寫、發送的「行動計畫」明確地煽動群眾暴力:「這些完全不是敵營所說的暴行。人民對抗他們痛恨的人,或報復那些有著可恨回憶的公共建築,我們不但應該寬恕,還要伸出援手。」[36] 偶爾他也支持刺殺,且準備好執行暗殺的人員。有一位追隨的革命者名叫科瓦萊夫斯基(Maxim Kovalevsky),當馬克思獲知一八七八年在柏林林登大道(Unter den Linden)謀殺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Emperor Wilhelm)未果的消息時,他也在場,並記錄了馬克思的暴怒,「不斷咒罵那個沒有實現他恐怖行動的恐怖主義者」。[37] 這樣的馬克思,要是權力穩固,似乎一定能製造異乎尋常的暴力與殘酷。但當然,他永遠都實現不了大規模的革命或暴力,所以才把壓抑的怒火寫進書裡,讓他作品的口吻永遠都是絕不讓步的極端主義,許多段落給人的印象是在盛怒時所寫的。不久之後,列寧、史達林與毛澤東會以更巨大的規模,實踐馬克思內心所感受到的兇殘,以及他的作品所散發出來的暴力。
實際上,馬克思覺得自己的作為合乎道德的程度有多少呢?無論是曲解真相或鼓吹暴力,都很難講。在某種意義上,他有強烈的道德感,他滿腔熊熊的欲望,想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但他還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裡嘲笑道德,他主張道德「不科學」,而且可能成為改革的障礙。他似乎認為人類的行為省去這一類形上學的改變,將能引起共產主義的出現。[38] 就像許多自我中心的人,他傾向於認為道德法則不適用於自己,或是有點將道德本身視同自己的利益。無疑地,他在無產階級身上看見利益,能共同擴張、實現他自己的看法,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Michael Bakunin)發現他「一直熱衷於為無產階級奮鬥,儘管當中參雜著個人的虛榮」。[39] 他一直都很自戀,有一封年輕時寫的、篇幅極長的信留存至今,假託是寫給父親的,實際上大概是寫給他自己的。[40] 他對於別人的感受與看法,都沒什麼興趣也不在意,不管在哪裡工作,他都想要獨力作業。他在擔任《新萊茵新聞》(Neue Rheinische Zeitung)的主筆時,恩格斯評論道:「編輯團隊的編制,完全是馬克思一人獨裁。」[41] 他沒時間也沒興趣了解民主,除了他給這個詞加上的特殊與造假的意義。任何一種類型的選舉他都厭惡──在從事新聞工作期間,他對英國普選不屑一提,僅僅視之為酒醉的狂歡會。[42]
有關馬克思政治目標與行為的聲明,有許多不同來源,而值得注意的是「獨裁者」一詞出現得十分頻繁。安納科夫在一八四六年說他是「民主政體獨裁者的體現」,另一個非常有智慧的普魯士警察,在回報馬克思在倫敦的言行時注意到:「他個性的特點是對權力沒有極限的野心與熱愛…… 是其黨羽的絕對主宰…… 他凡事親力親為,為自己的任務下指令,無法忍受不同意見。」鐵肖(他的邪惡副手)有一次故意灌醉馬克思,想讓他吐真言,接著給了他一個絕佳的描繪,說他「性格突出」,有著「極度的知識分子優越感」,以及「要是他的心比得上他的才智,那麼他所擁有的愛便與恨一樣多,我將願意為他赴湯蹈火」。可是,「他的靈魂裡缺乏高貴的品質。我確信危險的私人野心,會吞噬他內在所有的善良…… 他所有的努力,目標都是獲得個人權力」。巴枯寧對馬克思的最終評價也抱持相同看法:「馬克思不信神,但他很相信自己,並讓每一個人都會為他所用。他心中盈滿的不是愛而是仇恨,以及些許對人類的同情。」[43]
馬克思習慣性的發怒,他的獨裁氣息與他的仇恨,無疑反映出他的權柄意識,以及他無法行使更大權力的極度痛苦。他年輕時的生活放蕩不羈、無所事事、道德淪喪。在他的中年早期,他依然認為很難合理、有系統地工作,經常整夜坐著聊天,然後白天半睡半醒地躺在沙發上。到中年晚期,他作息變得比較規律了,但他在工作上從不自律。他還是對最輕微的批評感到憤慨。他與盧梭都具備的特質之一,就是喜歡與朋友和贊助人吵架,尤其在對方給予有益的建言時。當他忠誠的同僚庫格曼醫師(Dr Ludwig Kugelmann)在一八七四年建議,只要把生活打理得好一些,就能輕鬆完成《資本論》時,馬克思就此與他決裂,並使他蒙受無情的辱罵。[44]
他狂暴的利己主義,有生理與心理上的淵源。他過著非常不健康的生活,很少運動,口味很重,食量通常很大,菸抽得兇,酒喝很多,尤其是烈酒。結果他的肝臟不停出毛病。他根本不太洗澡或洗手、洗臉,這一點,加上他不當節食,或許解釋了他長達二十五年的皮下膿腫災難。膿腫加重了他天生的易怒,而且病情似乎在他寫《資本論》時最嚴重,「不管發生什麼事,」他在信中嚴肅地告訴恩格斯,「我希望資產階級只要存在,我就會想起我的惡性膿瘡」。[45] 膿腫的數量、大小與嚴重程度不一,但時不時就會出現在身體各個部位,包括他的臉頰、鼻樑、屁股(讓他無法寫作)和陰莖。一八七三年,這些膿腫因焦慮與怒火引發了神經崩潰,留下瘡瘢。
此外,他主要的憤怒與挫折,以及他對資本主義體制的深惡痛絕,或許根源是他特別不善理財,這讓他年輕時落入高利貸的手中。對高利貸怒不可遏的仇視,是他整部道德哲學真實的情感動力,可以解釋為何他對這個主題投入這麼多的時間與精神,又為何他整個階級理論都建立在反猶太主義的基礎上,以及為何他在《資本論》裡有一段冗長且激烈的篇章譴責高利貸──那是他從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一篇冗長的反猶太惡罵中挑選出來的。[46]
馬克思的財務困境始於大學,並持續了一生,這些困境源自於本質上幼稚的心態。馬克思隨意借錢、花掉,然後當沉重的貼現票據加上利息成了應付款項時,他的震驚與憤怒始終如一。就整體而論,他把「收取利息」視為以資本為基礎的任何制度的必備要素,而是違反人性的犯罪,其根本是人對人的剝削而他的整個制度,都是設計來消弭這一點的。但在他自身情況的特殊脈絡裡,他回應財務困境的方式,是去剝削每一個他能取得聯繫的人,首先是他的家人。錢主宰了他與家人的往來信件,他父親寫給他的最後一封信,是一八三八年二月。當時海因利希已經時日無多,反覆抱怨馬克思對家人漠不關心,只想得到幫助或是發牢騷:「現在你法學課程才過了第四個月,你已經花了二百八十塔勒(thaler),我整個冬天都沒賺這麼多。」[47] 三個月後他過世了,馬克思不打算去參加葬禮,反而開始對母親施壓。他已經接受了一種生活模式,向朋友借錢,再定期向家人討錢。他認為家人「相當有錢」,有責任援助他,讓他做重要的工作。除了斷斷續續的新聞工作(似乎政治目的大於賺錢),馬克思從來沒有認真找過一份差事。雖然他在倫敦(一八六二年九月)曾一度應徵過鐵路職員,卻因為筆跡太潦草而被打回票。馬克思不願意追求職業生涯,似乎是他的家人對他的討錢冷漠以對的主因,他的母親認定他只會越借越多,不但拒絕幫他償債,最後甚至完全斷絕供給,之後便甚少往來,她極度不滿地認為:「卡爾能累積資本的,只要他不光是寫跟資本有關的玩意兒。」
不過,偶爾馬克思會繼承到一筆不小的金額。父親的死為他帶來六千金法郎(Gold francs),他把一部分花在比利時工人的武器裝備上。他母親死於一八五六年,遺產比他預期的少,因為他本來以為也會繼承到向菲利普姨丈借來的錢。他一八六四年也從友人威廉(Wilhelm Wolf)的資產中,收到一筆可觀的金額。其他的收入是透過他的妻子與妻子的家人(她自己也帶了嫁妝來,包括一套銀製餐具、伯爵先祖傳下來的徽章大衣,家徽刀具與寢具)。他倆收到的財富,合理投資的話,足以供應舒適的生活,且實際收入從沒有低於每年二百英鎊,是技術純熟的工人平均薪資的三倍。但不管是馬克思還是燕妮都對錢不感興趣,只喜歡花錢。遺產與借來的錢一樣,都一點一滴地花掉了,他們始終都沒有多出一便士的餘裕。他們一直負債,經常債務沉重,除了銀製餐具,其他物品也定期送去當鋪,包括他父親的衣物。有一陣子馬克思外出時,只有一件褲子可穿。燕妮的家人和馬克思的家人一樣,拒絕再幫這位無可救藥、揮霍無度的懶惰蟲女婿一把。一八五一年三月,馬克思在寫給恩格斯的信中,說自己生了一個女兒,並抱怨:「我家連一枚錢幣都沒有。」[48]
那時,當然恩格斯已經是被剝削的新對象。從一八四○年代中期他們第一次相逢開始,直到馬克思過世,恩格斯都是馬克思一家的主要收入來源。他可能交出了自己收入的一半以上,但總額難以估算,因為在他提供金援的二十五年裡,金額都不固定。想必馬克思一再擔保下一輪捐款即將到來,很快就能讓自己回到正軌。這種關係是馬克思單方面的剝削,完全是不平衡的,因為他始終占據主宰的地位,有時還會囂張跋扈。難以理解的是,他們需要彼此,就像舞台上搭檔演出的喜劇演員,無法獨自表演,頻頻抱怨卻離不開對方。這種合夥關係在一八六三年幾乎瓦解,當時恩格斯覺得馬克思不顧他人感受地討錢太過分。恩格斯在曼徹斯特有兩間房子,一間是娛樂事業用的,一間給他的情婦瑪麗(Mary Burns)住。瑪麗去世時,恩格斯深感悲痛,卻因為馬克思冷酷無情的信(日期為一八六三年一月六日)而暴怒,信中只簡短對傷痛表達致意,然後馬上索討更多錢。[49] 沒有比這更能顯示馬克思的自我中心了,恩格斯冷淡地回了信,兩人差一點絕交。後來有些不同,因為這封信讓恩格斯徹底了解馬克思性格的極限。大概這一次,恩格斯發現馬克思永遠不會去找一份工作,或扛起養家的責任,或把事務理出任何一種條理,也發現自己唯一要做的就是定期給錢。所以在一八六九年,恩格斯賣掉事業,以確保年收入不低於八百英鎊,當中有三百五十英鎊撥給馬克思。因此,馬克思在他人生最後的十五年,是一個靠投資收益過活的「食利者」,享受著一種可靠的安全感。儘管如此,他花錢的速度大約是每年五百英鎊、甚至更多,他向恩格斯辯解:「以商業角度來看,這裡不適合純粹的無產階級體制。」[50] 所以馬克思繼續寫信,要求恩格斯施捨更多的錢。[51]
但是當然,馬克思揮霍成性又不願意工作,首要受害者是自己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妻子。燕妮.是社會主義者中最悲慘的、令人同情的人之一,她是在弗洛登山(Flodden)被殺的第二代阿蓋爾伯爵的後裔,有著明顯的蘇格蘭外貌,蒼白的膚色,綠眼,以及傳承自父系那邊的紅褐色頭髮。燕妮是個美女,而且馬克思愛她──他的詩可以佐證──她也熱愛馬克思,為了他跟娘家、婆家的人爭吵。一個像馬克思這樣自我中心的人,如何能產生這樣的愛情?我認為是因為他很強壯,很有派頭,青年時期相當英俊,儘管總是髒兮兮。特別是他很搞笑。歷史學家們很少注意到這個特質,而這個特質幫助解釋了他某種吸引力,此外他還有點神祕(這也是希特勒的才能之一,在私領域與公開演說上都是)。馬克思的幽默往往嘲諷又粗魯,儘管如此,他絕妙的笑話還是令人開懷大笑,如果他不幽默,他許多令人不快的特質,會讓他一個追隨者都沒有,女人們也會都背棄他而去。但笑話是打動女人最有效的方法,她們的人生經常比男人更艱難。馬克思與燕妮常常一起大笑,後來也正是馬克思的笑話,讓女兒們跟他的關係緊密。
馬克思很自豪妻子是蘇格蘭貴族後裔(他誇大這一點),以及普魯士政府高官暨男爵的女兒。一八六○年代他在倫敦發出自己印製的舞會邀請函,提到她「娘家姓氏是馮.威斯伐倫」。他常常聲稱,比起貪婪的資產階級(許多目擊者說,他說這個詞會刻意發出刺耳的聲音,以示蔑視),自己跟真正的貴族相處還比較融洽。但是跟一個沒有國家歸屬、沒有工作的革命者結婚的可怕現實,應該會使燕妮漸漸醒悟,寧可去跟一個心胸狹隘的資產階級安頓下來。從一八四八年之後至少十年,她的人生是一場夢魘。一八四八年三月三日,比利時發出馬克思的驅逐令。他當時被關押在監獄裡,燕妮也整夜在牢房裡,和一群賣淫者關在一起。隔天,這一家人被警察護送到邊境。隔年的大部分時間,馬克思不是在逃跑,就是在接受審訊。到了一八四九年六月,他已經窮到一無所有。七月時他向一位朋友坦白:「我太太的最後一件珠寶,已經拿去典當。」[52] 他維持志向的方法是荒謬的、長期的革命樂觀主義,他在寫給恩格斯的信中說:「儘管現況如此,但驚人暴動的革命火山,從未如此逼近。細節稍後詳談。」但是對燕妮來說,從來沒有那種慰藉,而且她當時懷孕了。他們認為英格蘭安全,卻也是窮困潦倒,現在她有了三個孩子,燕妮、蘿拉與艾德格(Edgar),並於一八四九年十一月生下第四個,取名蓋(Guy)或吉多(Guido)。五個月後,他們因為沒錢付房租,被趕出在切爾西的房間而流落街頭,當著(燕妮寫道)「切爾西那些暴民」的面前。他們把床賣了,才能付錢給肉舖、牛奶販、藥劑師與麵包店家,他們在萊斯克廣場(LeicesterSquare)發現避難所,在一幢骯髒的寄宿宿舍裡。那個冬天,嬰兒吉多在那裡夭折了。燕妮在那些日子留下許多絕望的記述,從此,她的情緒、她對馬克思的愛,便從未真正復原過。[53]
一八五○年五月二十四日,英國駐柏林的大使威斯特摩蘭伯爵(Earl of Westmoreland)拿到一份報告副本,這是一個機敏的普魯士警探,記錄以馬克思為中心的德意志革命分子的活動細節。當時燕妮忍受的生活,沒有比這份報告寫得更清楚的:
(馬克思)過著放蕩不羈的知識分子生活方式。洗澡、穿著整潔與更換內衣,是他很少做的事情,倒是經常喝醉。雖然他經常連著好幾天遊手好閒,但是當他有大量工作要做,也會日以繼夜賣力工作。他沒有固定的就寢與起床時間,經常熬一整晚然後在正午穿好衣服躺在沙發上,一直睡到傍晚,絲毫不受房間周遭來來去去的影響(他們一共只有兩個房間)…… 家具沒有一件是乾淨而完整的,每樣東西都破損、破爛與裂開,每樣東西都蒙上半公分厚的灰塵,亂到了極點。(客廳)中間有一張覆著油布的老式大茶几,上頭堆著手稿、書本跟報紙,還有孩子們的玩具,以及他妻子縫紉籃裡的碎布與破衣服,幾個邊緣有缺口的杯子、刀叉、油燈、墨水、平底無腳的酒杯、荷蘭陶製菸斗、菸草、菸灰…… 一個舊貨商店老闆如果把這些稀奇古怪的零碎物品分送給別人,也會感到羞恥。當你走進馬克思的房間,煙霧與菸草的熏氣會讓你眼睛流淚…… 每樣東西都很髒且布滿灰塵,所以坐下來便成了一個冒險之舉,這裡有一張三隻腳的椅子,另一張椅子孩子們正在玩煮飯遊戲。這張椅子剛好有四隻腳,是給訪客坐的,但孩子們的煮飯痕跡並未擦去,如果你坐下,便是拿褲子開玩笑。[54]
這份報告的日期是從一八五○年起,或許描述的正好是這家人財富水位的最低點。但接下來幾年他們又面臨其他的不幸打擊。取名為法蘭齊絲卡(Franziska)的女兒在一八五一年誕生,翌年夭折。兒子艾德格是馬克思最鍾愛的孩子,他叫他「小蒼蠅」,在骯髒的環境下罹患腸胃炎,死於一八五五年。這對兩人來說都是嚴重打擊,燕妮未曾忘懷,「每一天,」馬克思寫道,「我的妻子都告訴我她希望躺在墓穴裡」。另一個女兒愛琳娜已經三個月大了,但對馬克思來說兒子和女兒是不同的。他一直想多生幾個兒子,而現在一個都沒了,女兒對他來說除了當助手,沒有其他價值。
一八六○年,燕妮得了天花,外表留下了無法恢復的疤痕。從那時起,直到她一八八一年過世,她逐漸退居馬克思的人生幕後。一個疲倦的、幻滅的女人,慶幸著小小的恩惠:她的銀製餐具從當鋪贖回來了,她有自己的住所。這要感謝恩格斯,在一八五六年,這一家人才得以搬出倫敦蘇荷區(Soho),在哈弗斯托克丘(Haverstock Hill)葛拉夫頓街(Graften Terrace)九號租下一間房子;九年後,再次感謝恩格斯,他們租到一間更好的房子,梅特蘭公園路一號(I Maitland Park Road),從此僕人不再少於兩名。馬克思開始每天早上都讀《泰晤士報》(The Times),被選為當地的教區委員會。在晴朗的週日,他會舉家浩浩蕩蕩地散步到漢普斯特德荒野公園(Hampstead Heath),他自己帶頭,妻子、女兒與朋友們隨後。
但是馬克思的資產階級化(embourgeoisement)導致了另一種形式的剝削,這次是他的女兒們。他三個女兒都聰明伶俐。有人可能會覺得,這位革命家會為了彌補孩子們坎坷與窮困的童年,至少該跟隨自己激進主義的邏輯,鼓勵她們擁有自己的職涯。事實上他拒絕讓她們受足夠的教育,不准她們受任何訓練,完全禁止她們工作。以愛琳娜為例,她是三個孩子中最敬愛他的,她告訴女性主義作家施賴那(Olive Schreiner)說:「漫長、悲慘的年月,在我們之間投下陰影。」反之,女兒們一直都在家裡學鋼琴與水彩,就像商人的女兒一樣。她們長大之後,馬克思偶爾還會跟他的革命友人串遊酒吧。不過根據社會主義者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necht)的說法,他不准那些人在他的屋裡唱喧鬧、下流的歌曲,因為女兒們可能會聽到。[55]
後來他拒絕女兒們的求婚者,這些求婚者往往跟他一樣有革命背景,他無法阻止結婚,想辦法找麻煩,而且他的反對也讓對方留下了心靈創傷。他稱呼蘿拉的丈夫,來自古巴、有部分黑人血統的拉法格(Paul Lafargue)「非洲小黑人」或「大猩猩」。他也不喜歡小燕妮的丈夫龍格(Charles Longuet)。在他看來,這兩個女婿都是白痴:「拉法格是僅存的普魯東主義者,而龍格則是僅存的巴枯寧主義者──兩個都該死!」愛琳娜是么女,蒙受馬克思不准女兒們追求發展的磨難,而她的求婚者遭到了最大的敵意。她被教養要視男人──也就是她父親──為宇宙中心。或許並不意外的是,她愛上了一個比她父親更自我中心的艾威林(Adward Aveling),他是作家,並自稱是左翼政治工作者,卻是個玩弄女性的男人,依賴他人而生活,專門誘姦女演員。[56] 愛琳娜想當女演員,成為受害者也是意料之中,歷史上短暫而準確的諷刺場景之一,便是艾威林、愛琳娜與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一起在倫敦參加了劇本《玩偶之家》(ADoll’s House)的第一場私人朗讀會,這是易卜生巧妙地為了爭取婦女自由權而舉辦的,愛琳娜飾演諾拉(Nora)。馬克思死後不久,她馬上成為艾威林的情婦,從此成為受盡他折磨的奴隸,一如她母親受父親的折磨。[57]
然而,馬克思需要妻子的程度,或許比他願意承認的來得更深。一八八一年她死之後,馬克思便急遽走下坡,不再寫任何作品。他在歐洲多處礦泉治療地接受療程,到阿爾及爾(Algiers)、蒙地卡羅(MonteCarlo)及瑞士遊歷,追求陽光與潔淨空氣。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他很高興自己在俄羅斯的影響力日益茁壯:「沒有比我的成功更令人雀躍的事了。」到最後他的影響力引起毀滅,他自吹自擂:「我毀了一個政權,在英格蘭隔壁,是舊社會的真正堡壘,這讓我心滿意足。」三個月後他身著晨袍與世長辭時,還坐在爐火旁。他的一個女兒,小燕妮,在幾週之前也過世了。另外兩個女兒也很悲慘,愛琳娜被丈夫的行為傷透了心,一八九八年在自殺時服用過量鴉片而死,而一起自殺的艾威林卻逃過一劫。十三年後蘿拉與龍格也約好自殺,而他們成功了。
不過,這個悲劇家庭有一個令人好奇、默默無名的倖存者,是馬克思對個人的剝削行為裡,最異乎尋常的一個。他在研究大不列顛資本主義者一切惡行中,列舉了許多工人低薪的例子,但他沒有找到出任何一個不支薪的例子。但這樣的工人確實存在,而且就在他家裡──馬克思帶領家人進行他們莊重的週日散步時,負責殿後、攜帶野餐籃與其他重物的,是一位矮胖的婦女,叫作海倫(Helen Demuth),他們一家都叫她「小莉娜」,她一八二三年出生於農家,八歲就進了馮.威斯伐倫家做保母,她一直受雇但沒收到任何報酬。一八四五年,男爵夫人擔憂已嫁作人婦的燕妮,於是把當時二十二歲的小莉娜送過去,好分憂解勞。小莉娜從此便待在馬克思家,直到一八九○年過世。愛琳娜說她是「對別人最溫柔的人,雖然她終身禁欲」。[58] 她異常勞苦,不但要煮飯跟刷洗,還要管理一家的預算,因為這燕妮處理不來。馬克思從未付過她一分錢,一八四九至五○年間,在他們一家存亡最黑暗的時刻,小莉娜成了馬克思的情婦,而且懷了一個孩子。當時小吉多剛夭折,燕妮也再度懷孕。這整家人的居住空間只有兩個房間,而小莉娜的情況,馬克思不僅瞞住了燕妮,還瞞住了絡繹不絕前來造訪的革命人士。最後燕妮還是發現了,或者是被通知了,這是她所有的不幸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可能甚至讓她對馬克思的愛到此為止。她說「我不該繼續想著這件事,儘管於公於私,這件事都大大地加重了我們的傷痛」。這是一八六五年她在自傳草稿上所寫的內容,這份三十七頁的草稿,只有二十九頁保留下來:其餘描述她跟馬克思爭吵的內容都遭到破壞,可能是愛琳娜做的。[59]
小莉娜的孩子於一八五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出生,地址是蘇荷區迪恩街(Dean Street)二十八號。[60] 是一個兒子,登記名字是亨利(Henry Frederick Demuth)。馬克思拒絕承認,從那時起直到他過世,都斷然否認自己是生父,他或許會希望自己能做一個盧梭,把孩子丟在孤兒院,或是讓孩子永遠送養。但小莉娜的個性比盧梭的情婦強勢多了,她堅持這是她的兒子。這個男孩被送給一個叫做路易斯(Lewis)的工人階級家庭領養,但獲准來拜訪馬克思家。但他被禁止出入前門,並被限制只能在廚房和母親會面。馬克思很害怕亨利的身世被發現,這將為他革命領袖與先知的身分帶來致命傷害,他留存下來的信件中,有一處隱約提及此事,其餘的信被許多人動過手腳,以封鎖消息。他最終強迫恩格斯認亨利當私生子,為家族裝幌子,像是愛琳娜就信了。恩格斯儘管一如既往,準備好為了共同工作而服從要求,卻沒有將這個祕密至死都守口如瓶。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死於喉癌,臨終前,他無法說話,卻不願意讓愛琳娜(暱稱杜西)繼續認為她的父親一生清白,他在一片板子上寫道:「亨利是馬克思的兒子,杜西想為其父造神。」恩格斯的祕書兼管家弗雷伯格(Louise Freyberger),在一八九八年九月二日寫給社民黨領袖倍倍爾(August Bebel)的信中,說恩格斯已經說出真相,並補充說:「亨利長得和馬克思簡直一模一樣,典型的猶太臉孔,深藍色頭髮。只有盲目的偏見才會在他身上看見任何像將軍(她都這樣稱呼恩格斯)的地方。」愛琳娜接納了亨利是她同父異母的兄弟,並漸漸喜愛他,她寫給他的九封信都留存至今。[61] 但是她沒有為他帶來任何運氣,因為她的愛人艾威林借走了亨利的畢生積蓄,從沒還過錢。
小莉娜是馬克思認識的人裡面,唯一一個工人階級的成員,是他真正接觸過的無產階級者。亨利可能也算一個,因為他長大後成為工人階級小伙子,他在一八八八年三十六歲時,得到夢寐以求的執照,成為合格的機工。他差不多一輩子都在國王十字(King’s Cross)與哈克尼(Hackney)這兩間公司,而且是一個工會的長期成員。但馬克思不認識他,只見過一次面,推測是亨利從廚房外的階梯要走進來,而他根本就不知道這位革命哲學家是他的父親。他在一九二九年一月過世,以馬克思的眼光來看,當時無產階級的獨裁政府已然成形,令人喪膽,而史達林──這位達成馬克思所嚮往的絕對權力的統治者,對俄羅斯農民災難性的暴行,才正要開始。
1 國際工人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又稱「第一國際」,後者是第二國際成立後才出現的名稱。
2在法國大革命時,群眾把巴黎的路燈視為政府的象徵物,於是摧毀路燈並把受刑者吊在燈柱上。
3 太平紳士(Justices of Peace)為英法系地區的體制,由政府委託民間人士處理一些簡易法律程序。
4 綠磨坊街(Rue Des Moulins)在今日的巴黎歌劇院商圈附近,曾聚集許多偉大的藝術家。
5 摩爾人(Moor)一詞當時在歐洲使用廣泛且略帶貶義,一般指穆斯林。
第四章 易卜生:在家也配戴勳章的偉大劇作家
「他微微噘起的雙唇像刀身一樣薄…… 我站在一堵封閉的山牆前面,一道費解的謎團前 面。」 ── 約翰.包爾森,被易卜生攻擊的作家
所有的寫作都很費力,創意寫作更是單調乏味的苦差事中,最費力的一種。創意上的革新,尤其是從根本上翦除禍根的革新,需要額外更多的專注與心神。而一生不斷開拓創意邊界,意味著此人必有某種程度上的自律。在知識產業裡,鮮少有人能掌握這種自律。不過,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sen)的作品就有著這樣前後一致的模式,很難想出還有哪個作家,在任何領域、任何年齡上更平順地致力於此了。他不光發明了現代戲劇,所寫出的一系列劇本,還形塑出所有現代劇作的重要環節。他發現西方的舞台劇空洞無力,將之改造成豐富又有力量的藝術形式,不只風行本國,還風靡了全世界。此外,他不只改革了他的藝術,也扭轉了整個世代對社會的想法,而且是一個世代接著一個世代。盧梭在十八世紀末的作為,恰是易卜生在十九世紀末的貢獻。盧梭追求的是男女回歸自然,在自然當中參與集體的革命,而易卜生則是鼓吹個人起來反抗歐洲舊制度的壓抑與歧視,這種壓抑與歧視確實主宰著每一個小城鎮裡頭的每一戶人家。他教導人們,尤其是女人們,個人的善惡觀念與對自由的看法,在道德上都優先於社會對他們的要求。透過這麼做,他參與了一場意見與行為的革命,這場革命始於他在世期間,然後一直持續到現在,時不時就會冒出來發作一陣。早在佛洛伊德以前,他便指出「縱容社會」1 的基本原則。可能連盧梭、馬克思,在反對政府的作用上,對人民都沒有這麼大的影響力。他和他的作品,形塑出現代拱門的拱頂石。
……
1 縱容社會(permissive society)是英國十九世紀六○年代以來的社會態度,認為只要不傷 害別人,怎麼做都百無禁忌。
第五章 托爾斯泰:熱愛「亞威視角」的沒落貴族
「從沒遇過這麼難相處的人,逼人的表情,兩三句惡毒的評論,就足以搞瘋一個人。」 ── 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的好友
在我們檢視的知識分子當中,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最有企圖心。他的膽大妄為令人敬畏,有時還挺嚇人的。他相信,藉由他本身智識的應變能力、藉由他所感受到的內在精神力量之美善,他就能實現社會的道德轉化。他的目標就如他所言,是「讓基督的神國,在地上的王國降臨」。[1] 他視自己為「知識分子中的使徒繼承者」,這份知識分子名單包含摩西、以賽亞、孔子、早期的希臘人、佛陀、蘇格拉底,一路向下到巴斯卡(Pascal)、斯賓諾莎(Spinoza)、費爾巴哈(Feuerbach)等哲學家,還有那些沒有名氣,卻用思想與話語勸說人生意義的人。但托爾斯泰不願維持「沒有名氣」的狀態,他的日記透露了這一點,早在年紀輕輕的二十五歲,他就意識到一種特殊權力與居高臨下的道德主宰力量。「今天讀了一部描述天才的文學作品,激發了我的信念,那就是在工作能力與對工作的渴望這兩方面,我都是卓越的人」、「我還沒遇過在道德上跟我一樣良善的人,我人生中的每一個時刻都在反省並積極向善,準備好為此犧牲一切」,他感覺自己的靈魂「無上高貴」。他對於自己的品德無法使他人肯定而挫折:「為什麼沒有人愛我?我不是傻子,不是殘障,不是壞人,不是無知的人。無法理解。」[2] 無論托爾斯泰如何努力同理他人、參與他人,他一直感受到他人某種程度上的冷漠,很奇怪,他感覺自己在他們當中,就像坐在法官席上,正在進行道德審判。當他成為一個小說家、甚至是最偉大的小說家,他毫不費力就奪取了這種亞威的權力。他告訴馬克西姆.高爾基(Maxim Gorky):「我在寫作時,若是突然同情起某些角色,便給他們添加一些良善品性,或是去除別的角色的良善品行,這樣跟別人相比,他看起來就不會太過黑暗了。」[3] 當他成為一個社會改革者,這種與亞威的一體感也變得更加強烈,因為他的計畫和神一樣廣大,一如他所界定的:「渴求普世的福祉…… 這我們稱之為亞威。」他確實感覺自己擁有神性,在他的日記裡提到:「求祢幫助,天父,來與我同在。祢已與我同在。你已成為『我』。」[4] 但是托爾斯泰與亞威,很難同時存在於同一個靈魂,因為就像高爾基注意到的,托爾斯泰極端懷疑他的造物主。他說,這讓他想到「一個山洞裡的兩隻熊」。有時托爾斯泰似乎認為自己是亞威的兄弟,更確切地說,是祂的長兄。
……
舊秩序下的貴族們都很難擺脫這個概念:寫作是地位低於他們的人做的事。拜倫從未把作詩當成他最重要的工作,他最重要的工作是幫助歐洲人民實現獨立,他覺得自己受到呼召出來帶領人民,而這跟他的階級相稱。托爾斯泰也是如此,他感受到的呼召確實比帶領人民更多:那是傳教,有時則扮演彌賽亞。那麼,他把時間拿來做了什麼,寫作嗎?他告訴詩人費特(Fet),「寫小說愚蠢又丟臉」,注意第二個形容詞。這是一個不時出現的基調,認為藝術是對天賦的一種粗暴的濫用,當他突然想要破除傳統時,便會將天賦用於寫出更強硬的語言。因此隨著他年紀漸長,他不時會宣布要放棄藝術,轉而發揮道德領導力。
如今看來,這是自欺欺人的慘案。值得注意的是,托爾斯泰是世上最會替自我著想的人之一──包括盧梭在內──且其大部分小說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以他自己為中心,但他卻明顯缺乏自知之明。他身為作家最夠格這麼做,而且他寫作時,對周遭的人與社會來說最無害。但他並不希望成為作家,這無論如何是褻瀆聖靈的,他想要的是領導,即使他毫無這方面的能力,只有意願。要作個先知、建立一個宗教、改變這個世界,他在道德與智識上都不具資格。所以偉大的小說一直沒寫出來,他卻帶領著,或者不如說是拖著他自己跟他的家人,走進混亂的荒野。
……
然而,更嚴重的是托爾斯泰獨裁主義的觀點:只有他能解決人世間的苦難,並且拒絕參與他沒有親自規畫或掌控的任何救濟活動。他的自私甚至包含他的慈善事業,他的人生有好幾次態度大轉變,包括在大部分的政治問題、土地改革、殖民地的開拓、戰爭、君主制、國家、所有權等議題上,他說法自相矛盾的清單不計其數。但有一件事始終如一,他拒絕親自參與任何讓俄羅斯產生革命的組織規畫──即從根源來解決問題──而且他以日益激烈的憤怒,譴責自由主義的「進步」是錯覺,實際上是純粹的邪惡。他痛恨民主,鄙視議會,說俄羅斯國家議會杜馬(Duma)的議員們是「小孩在玩大人的遊戲」。[46] 他主張沒有議會的俄羅斯,比有議會的英國更加自由,而且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不是回應議會改革。托爾斯泰特別討厭俄羅斯的自由傳統,在《戰爭與和平》中他公開嘲笑首位自稱是革命家的斯彼蘭斯基(Speransky)伯爵,他讓安德烈(Andrew)親王這樣評論斯彼蘭斯基的新國會提案:「對我來說有什麼要緊的…… 這一切能讓我更快樂或更好嗎?」這是俄羅斯歷史中陰暗的事實,長達半個世紀,這個國家最偉大的作家,板著臉堅決反對為帝制做任何制度面的改革,並極力阻礙、指責試著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加文明的那些人。
但是托爾斯泰有別的選擇嗎?要是他像狄更斯、康拉德(Conrad)等其他偉大的小說家一樣,認為結構性改善的價值有限,需要改變的是人心,那還比較說得通。但是托爾斯泰在強調個人道德需要提升的同時,卻不願意到此為止:他不斷暗示眼下迫切需要某些巨大的道德變遷,必須改變這個世界並建立一個神聖的王國。他自己烏托邦式所做的努力,是在預示這場千禧年主義式的太平盛世 3。但在這種憧憬的背後,並沒有嚴肅的思考。這多少有某種大變革的純粹戲劇特質在裡頭,就像我們已經看過的,馬克思革命理論中的詩化異象。
此外,托爾斯泰也跟馬克思一樣,對歷史的理解有缺陷。他認識的歷史不多,對於歷史大事件如何發生沒有概念。就像屠格涅夫悲嘆的,《戰爭與和平》裡那些令人尷尬的、有關歷史的冗長訓話,暴露了自學者的特點。它們是「滑稽的」,純粹是「狡辯」。福樓拜在寫給屠格涅夫的信中也曾驚愕地提到:「他的哲學!」[47] 不過,我們讀這部偉大的小說,不是因為其中的歷史見解。托爾斯泰是個決定論者(Determinist),反對個人主義。認為事件是由權勢者深思熟慮的決策形塑而成,這樣的概念對他來說是天大的錯覺。那些貌似掌權者的人,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更別說是策劃事件的發生了。只有未察覺的活動是重要的,歷史是芸芸眾生上百萬個決策的產物,而這些人無法控制他們正在做的事情。某種程度而言,儘管途徑不同,但此一概念與馬克思是相同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導致托爾斯泰有這種想法,也許這就是他對俄羅斯農奴存的浪漫想法,認為他們是最終的裁決者與力量。無論如何,他認為冥冥之中的規則,實際上主宰我們的人生。這些規則不為人所知,甚至可能不可知。因此,與其面對不合意的事實,不如假裝歷史是偉人與英雄行使自由意志而形成的。實際上托爾斯泰一如馬克思,都是諾斯底派 4,拒絕接受事情如何發生的表面解釋,尋求表面之下神祕機制的知識。這種知識是由整個團體直觀、共同感知到的──這個團體,對馬克思來說是無產階級,對托爾斯泰來說是農奴。當然,他們需要解釋者(馬克思)或先知(托爾斯泰),但本質上是集體力量的「正當性」在推動歷史巨輪的運轉。在《戰爭與和平》中,為了證明歷史如何運轉,托爾斯泰扭曲歷史記載,一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斷章取義、竄改政府當局的藍皮書。[48] 托爾斯泰重新設計並利用了拿破崙戰爭,就像馬克思歪曲了工業革命以符合他強求制度一致性的歷史決定論。
所以,當托爾斯泰面對俄羅斯的社會問題,會傾向於集產主義者的解決方案,也就不令人意外了。早在一八六五年八月十三日,他在思考饑荒時,便在筆記本寫下:「俄羅斯全國的一大任務,是賦予世界新的概念,一個沒有私有土地的社會結構。只要人類的家庭繼續存在,比起英國的憲法,『財產權是竊盜!』將依然會是更大的真理…… 俄羅斯的革命只能以此為基礎。」[49] 四十三年後,他偶然發現這個筆記內容,於是驚嘆自己的先見之明。當時托爾斯泰已經和馬克思主義者及最初的列寧主義者站在同一陣線,……
…… 無論如何,他不會把馬克思主義者視為敵人。真正的敵人是西式民主,議會政體的自由主義,隨著那些人的理念正在開枝散葉,他們將腐化這整個世界。在他晚年的作品《給中國的一封信》(A Letter to the Chinese)與《俄國革命的意義》(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都寫於一九○六年)中,堅定地認定他自己與俄羅斯是屬於東方。「最重要的是,」他寫道:「西方人可以、也該成為東方人典範的東西,不是該有何作為,而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該有的作為才對。追求西方諸國的道路將直接通往毀滅。」對世界危害最大的是大不列顛與美國的「民主制度」,這與國家的宗教狂熱以及實施制度化的暴行密不可分,俄羅斯必須反對西方,放棄工業,廢除國家並擁抱不抵抗政策(non-resistance)。
根據俄羅後來發生的事件,這些想法給我們古怪的感覺,而且跟當時的實際情況也全然脫節。一九○六年的俄羅斯,工業化比其他國家迅速,其後成為史達林將該國極權化的墊腳石。然而當時,托爾斯泰的人生已經走到了對真實世界不再接觸、甚至不再感興趣的階段。他已經在自己的亞斯納亞 — 波利亞納世界裡,居住、占據並實行某種程度的統治。他認同國家權力遭到腐化,這也是他轉而反對國家的原因,但他沒有發現一些顯而易見的事實──例如,這對索妮亞來說很明顯──受腐化的權力有很多種形式。一個偉人、預言家、先知,對其追隨者也行使了某種權力,而追隨者的諂媚奉承、卑躬屈膝,特別是討好恭維之舉,敗壞了這個人。
早在一八八○年代中期,亞斯納亞 — 波利亞納就成了一個聖殿,各式各樣的人前來尋求指引、幫助、安定,以及神蹟般的智慧,或是前來訴說他們陌生的觀點──包括素食主義者、斯威登堡教徒(Swedenborgians)、親餵母乳的支持者,以及美國土地改革者亨利.喬治(Henry George)、修道士、宗教領袖、喇嘛與僧侶、和平主義者與逃兵,怪人、瘋子與慢性病患。此外,托爾斯泰還有一支由隨從與門徒組成的固定班底(不過成員一直變動)。無論如何,他們全都視托爾斯泰為精神領袖,部分視之為導師、主教、彌賽亞。就像一七八○年代朝聖者對盧梭的墳墓所做的事那樣,訪客在亞斯納亞 — 波利亞納大庭園的涼亭裡留下銘刻或塗鴉:「死刑降臨!」、「全世界的工人聯合起來,向一位天才致敬!」、「願李奧.尼古拉耶維奇延年益壽,長命百歲!」、「圖拉的現實主義者向托爾斯泰伯爵致意!」等等。托爾斯泰在享譽盛名的晚年確立了一種模式,(我們將會看見)這種模式在享譽國際的重要知識分子中一再重現:他成立一種類政府組織,處理世界各方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並與國王、總統們通信,提出抗議、發表聲明,最重要的是署名簽字,為了宗教的或世俗的、善良的或邪惡的理由,把自己的名字借出去。
……
托爾斯泰的例子再次說明,當知識分子以他人為代價追求抽象理想,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歷史學家喜歡將之視為從微小個人身上發端的序幕,開啟了一個無盡的巨大國家災難,這個災難很快就會吞沒整個俄國。托爾斯泰試著實現他認為非做不可、全面的道德改革,結果毀了他的家庭,也毀了他自己。然而,他盼望並預測──並透過作品大力支持──俄羅斯本身的千年變革,不會是他瞧不起的那種漸進、困難的改革,而會是一場火山爆發般的災變。這個災變在一九一七年到來,他並未預見這些事件的結局,他若親眼見到,應該會嚇到不寒而慄。這場變革使他所寫的社會重生理論變成謬論,他心愛的神聖俄羅斯毀滅了,而且似乎是永遠的毀滅。
令人痛恨而又諷刺是,後來新耶路撒冷 6 的主要受害者,是他所愛的農民,兩千萬的農人被大屠殺,成為這些理念祭壇上的犧牲。
1 普希金(Pushkins)為俄國小說家;奧斯特羅格拉德斯(Ostrograds)為俄國數學家;斐拉瑞多夫斯(Filaretovs)為莫斯科主教。
2 尼古拉耶維奇是他的中間名,他或許想藉此隱去「托爾斯泰」這個響亮的姓氏。
3 千禧年主義(millennialism)源於某些基督教派,認為世界有一個長度為一千年的時間循環,相信在善惡混戰與審判之後會有一個黃金時代:全球和平來臨,地球將變為天堂。
4 諾斯底派(Gnoastic)又稱為靈知派,基本上是質疑世界、歷史和群體的。
5 黑色百人團(Black Hundred)是二十世紀初俄羅斯的極端民族主義團體。
6 新耶路撒冷公社(New Jerusalem Commune)是在托爾斯泰思想下創立的勞動公社,在一九八九年被清算。
第六章 海明威:嗜酒如命的大師/騙子
「如果一個人健康,那麼他當一個支配者來影響別人也很好,可是如果他的靈魂乾枯腐朽,你要怎麼鼓起勇氣告訴他,他現在惡臭難當?」 ── 格雷葛利,海明威之子
儘管整個十九世紀,美國在各種數據與國力上都有所成長,並在世紀結束時,儼然成為世界最大、最富強的工業強權,但許久以來,其社會並未開始產出我所描述的那種知識分子。這有幾個理由:獨立後的美國從未擁有過舊的政治與社會體制,舊制度的基礎是一個擁有特權的統治集團,而不是「自然公正」(natural justice)的古老司法原則。沒有不理性、不公正的既有階層,讓新的知識分子去策畫出基於理性與道德的太平模式來取代。恰恰相反:美國本身製造了一場對抗舊秩序不公義的革命,其憲法是由具有最高的才智、哲學愛好與道德地位的一群人,基於理性與倫理原則,並根據早期經驗制定、撰寫、頒布與修正而來的。因此,統治階層與知識階層之間沒有裂痕:他們是一體的。於是,就像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提到的,美國沒有制度化的神職階層,也就沒有反教權主義,而這是歐洲知識分子產生騷動的源頭。宗教在美國很普遍,但是掌控在無聖職者的手中。這個國家本身關切的是行為,而非教條。這是出於自發性與多面向的,也因此所展現的是自由而非限制自由。最後,美國滿地都是機會,那裡土地便宜且資源充裕,沒有人必須貧窮,沒有明目張膽的不公不義,但在歐洲,正是這種現象激發了受良好教育的聰明人擁抱激進思想。美國沒有呼求上天報仇的罪孽──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大部分人太忙著賺錢與消費,開發與兼併,沒空對他們社會的基本假設提出質疑。
早期的美國知識分子,例如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他們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歐洲,帶著歐洲的腔調與習慣,作風與內涵,是文化殖民主義活生生的遺產。本土的、獨立的美國知識分子潮流的出現,是為了對歐文及其同類卑躬恭維的反抗。此一風潮第一位與最具代表性的倡議者──十九世紀美國知識分子的原型──是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他宣告他要驅走從美國上下榨取的「歐洲寄生蟲」,「用對美國的熱情趕走對歐洲的熱情」。[1] 他也曾造訪歐洲,卻帶著批判和否決的心情。他堅持美國主義的社會立場,獲得越來越廣泛的認同,隨著他年紀增長,社會與他的主張也益發緊密,他和歐洲知識分子的觀點也完全相反。愛默生於一八○三年在波士頓誕生,父親是論派(Unitarian)的牧師。他原本也成為了牧師,但後來離開牧師職務,理由是無法克盡職責,好好主持聖餐禮。他遊歷歐洲,發現了康德,歸國後在麻薩諸塞州的康科特(Concord)落腳,發展出美國第一個本土哲學運動:超驗主義 1,並於一八三六年出版了第一本著作《自然》(Natur)簡述此一概念。它是一部新柏拉圖哲學的著作,帶點反理性、神祕主義,並也觸及浪漫主義的,以及最重要的是它的曖昧朦朧。……
……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馬克思正在發展與鼓吹自己的學說,很難想得出有比愛默生的理論更南轅北轍的任何理念了。而愛默生在此領域的實際經驗,一再反駁馬克思認知的資本主義必然走向。業主與經理人不但不反對這種對啟蒙的追求,而且積極發揚。……
……
美國當時的經濟發展,文化與智識生活看起來顯然和諧一致,我們應該把厄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放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第一眼要看出他是知識分子並不容易,但更仔細審視,會發現他不但呈現所有知識分子的主要特質,而且是以特殊的美國式混合,掌握這些特質到非凡的程度。此外,他還是個深具原創力的作家,追隨他的美國人,以及整個英語世界的人,都因他而改變了表達自我的方式。他開創了新的、個人的、世俗的,以及非常當代的道德風格,這種風格純粹是美國原創,但本身能輕易轉化為多種文化。他把一些不同的美國態度熔接起來,並把自己變成這些態度的原型化身,這樣他就能賦予美國一個時代的形象,就像法國一七五○年代的代表伏爾泰,或是英國一八二○年代的代表拜倫。
……
真的?假的?還是言過於實?沒人知道。海明威與自身相關的敘述,以及他所寫的、少量跟別人有關的敘述,能在未經確認的情況下,被當成事實接受。儘管「真實」在他小說的道德觀裡具有核心地位,但他還是有典型知識分子的信念。在他的案例裡,「真實」必須願意為他的自我效勞。他認為說謊是他作家訓練的一部分,有時甚至以此自豪。他有意識地撒謊,也會不經思考地說謊。有時他肯定知道自己在說謊,就如同他在迷人的《士兵之家》(Soldier’s Home)中,以當中的角色克雷布斯(Krebs)清楚表明的,他寫道:「最好的作家是說謊家,這並不奇怪。他們主要販售的,就是謊言或虛構…… 他們經常下意識地說謊,然後痛悔自責地記住他們的謊言。」[35] 然而,證據顯示,早在海明威以書面辯護其謊言乃職業所需之前,他就已經說了很久的謊。他五歲就說謊,宣稱自己在沒有別人幫忙下拉住一匹衝撞的馬。他告訴雙親已經跟電影女演員梅.瑪許(Mae Marsh)訂婚,不過他除了在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Birth of a Natio)上見過她之外,根本未曾謀面。這個謊話他也跟堪薩斯城的同事說過,加上訂婚戒指價值一百五十美元的細節。許多露骨的謊言一目瞭然又令人尷尬,在他十八歲時,他告訴朋友他抓到一隻魚,但顯然是上市場買來的。他說了一個詳盡的故事,是他在芝加哥當職業拳擊手,鼻子都被打斷了卻還是繼續搏鬥。他捏造自己有印度血統,甚至聲稱自己有幾個印度女兒。他的自傳《流動的饗宴》相當不可靠,而且就像盧梭的《懺悔錄》,看似坦率的地方最危險。他經常編造跟父母與姐妹有關的謊言,有時沒有明顯理由,例如他說他的妹妹卡蘿(Carol)曾在十二歲被一個性反常的人強暴(相當虛假),後來又宣稱她離婚甚至死了,但實際上她開心地嫁給海明威討厭的嘉迪納先生(Mr Gardiner)了。[36]
許多海明威最複雜、並一再重申的謊言,與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服役有關。當然,大部分的士兵,包括英勇的士兵,也會說一些戰爭的謊言。詳加調查海明威所經歷的生活,勢必將揭開某些他玩忽職守的真相。[37] 儘管如此,海明威捏造在義大利發生的事,還是非常無恥。起初他說自己自願從軍,但因為視力差而遭到拒絕,但這沒有出現在記錄文件中,而且也不大可能發生。實際上,他是非戰鬥人員,而且是他自己選的。……
戰爭暴露了海明威是個說謊家。在西班牙,他嫉妒特派記者馬修斯的優越能力,他在一封寄回美國的信中,對特魯埃爾(Teruel)前線的報導謊話連篇:「拿到戰爭第一則報導發到紐約,比馬修斯早了十個小時。然後回去,和步兵團一起全面進攻,進入市區,跟隨著一個爆破連和三個步兵部隊,排成縱隊前進,返回,整理出天殺的、逐戶爭奪的戰爭報導,準備用電報發出……」[38] 他還謊稱自己是一九四四年第一個進入被解放的巴黎的人。情欲也暴露了海明威是個說謊家,他最仔細推敲、經常一說再說的義大利謊言之一,便是他當過一個西西里旅館女老闆的性囚犯,她藏起他的衣服,使他不得不與她私通了一週。他告訴貝倫森(Bernard Berenson),寫完《太陽依舊升起》,他與一個女孩打得火熱,但他妻子突然回家,他被迫把那女孩偷偷從屋頂送出去。這全都不是真的。他對一九二五年在西班牙潘普洛納(Pamplona)與里布(kike [Harry] Loeb)知名的爭風吃醋也說了謊,他說里布有一把槍,揚言要開槍打他(此事在《太陽依舊升起》被美化了)。他對每一段婚姻,離婚與協議都說了謊,不光是對女人說謊,對他母親也一樣。他對第三任妻子瑪莎.蓋爾霍恩(Martha Gellhorn)有關的謊特別膽大,她因此不屑一顧地說他是「繼孟喬森之後最大的說謊家」3。和其他小說家/說謊家一樣,海明威留下許多假蹤跡:某些他最突出的故事,以他自己壓倒性的內部證據來看,儘管看起來是自傳,卻可能純屬杜撰。只能說,海明威不怎麼尊重真實。
結果,他恰恰為一九三○年代那「卑微、詐欺的十年」做好了準備。海明威從未對政治信念抱持一致的立場。他的道德觀只跟對自我忠誠有關。曾是他朋友的多斯.帕索斯認為,年輕時的海明威「是我遇過揭露政治傾向的人裡面,腦袋最狡猾的」。[39] 但很難為此找到多少證據。在一九三二年的選舉裡,海明威支持社會主義者尤金.德布思(Eugene Debs),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他已經成為共產黨路線大部分議題的積極倡導者。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發行的共產黨黨報《新群眾》(New Masses)上,他投搞了一篇激烈的文章《是誰殺了老兵?》(Who Killed the Vets?),指責政府應該為佛羅里達州颶風負責。那場災禍造成受雇於聯邦工程、由退役軍人轉職的四百五十名鐵路工人死亡,這是共產黨典型宣傳鼓動(agitprop)的行動。在這十年裡,海明威似乎一直認為,共產黨是對抗法西斯聖戰唯一合法、可靠的領導者,批評或參與其掌控之外的活動,都是背叛行為。他說不管是誰,只要反對共產黨路線,「不是傻子就是惡棍」,當他發現由《君子》(Esquire)雜誌發行的新左翼雜誌《肯恩》(Ken)不是共產黨媒體,他不願讓他的名字出現在雜誌刊頭。
此一態度主宰了他對西班牙內戰的回應──作為寫作的素材,他以職業立場樂見其成,他說:「內戰是對作家來說最好、也最完整的戰爭。」[40] 但很奇怪,因為他的道德規範對於忠誠的衝突、傳統權力與不同的正義概念制定了詳盡條款,而他卻全盤接受共產黨對戰爭粗糙行事的路線。他四度自己花錢到前線去(一九三七年與一九三八年的春秋兩季),而他還沒離開紐約時,便已經決定了內戰的議題重點,並已經和帕索斯、海爾曼與麥克列許(Archibald MacLeish)一起簽約了一部宣傳電影:《戰火中的西班牙》(Spain in Flames)。他寫道:「我的同情永遠是給那些被剝削的勞動人民而非在外的地主,即便我跟那些地主們一起喝酒、射鴿子。」共產黨是「這個國家的人民代表」,這場戰爭是「人民」與「在外地主、摩爾人、義大利人和德國人」的鬥爭。他說他喜歡並尊敬西班牙共產黨,他們是此一戰爭中「最好的人」。[41]
根據西班牙共產黨的政策,海明威的路線是降低蘇聯的重要性,特別是在指導西班牙共產黨與西班牙共和國之間血腥內鬥的殘酷行為上。這導致他與帕索斯難看的決裂。帕索斯的翻譯是羅夫萊斯(José Robles),後者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特別研究員,在戰爭爆發時加入共和軍,也是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首領安德烈斯.寧(Andres Nin)的朋友。羅夫萊斯也曾經擔任蘇聯軍事使節團在西班牙的首腦貝津(Jan Antonovic Berzin)將軍的翻譯,因此知道一些莫斯科與馬德里國防部的祕密往來。貝津已經被史達林暗殺,史達林後來也下令西班牙共產黨要清算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安德烈斯.寧被凌虐至死,上百名黨員被捕,被控從事法西斯活動,並遭到處決。
羅夫萊斯被指控為是間諜,並因此被祕密處決。帕索斯對他的下落不明越來越擔憂,海明威認為自己在政治事務上非常老練,而帕索斯是個天真的菜鳥,因此對這種焦慮嗤之以鼻。當時海明威住在馬德里的蓋洛德飯店(Gaylord’s Hotel),那是當時共產黨的首領常去的地方。他詢問密友金塔尼利亞(Pepe Quintanilla)發生了什麼事(此人後來被證實是共產黨大部分處決的行刑者)得到的答案是:羅夫萊斯還活著,而且過得很好,他當然會被逮捕,但肯定會得到公正的審判。海明威也這麼認為,並這樣告訴帕索斯。但實際上羅夫萊斯已經死了,而當海明威後來發現這個事實──從一個剛抵達馬德里的記者那裡得知──他告訴帕索斯,顯然這是罪有應得,只有傻子才不這樣認為。帕索斯非常憂傷,拒絕接受羅夫萊斯有罪,並且公開指責共產黨員。這帶來海明威的訓斥:「西班牙正在打人民與法西斯主義者之間的戰爭,而你過去站在人民這一方。如果你對共產黨人心懷怨恨,或者是為了錢,以為有正當理由抨擊,那我認為為了還在打仗的人民,你至少應該搞清楚事實。」但結果證明搞清楚事實的是帕索斯,海明威才是那個天真、愚鈍、被騙的人。[42]
他一直維持這個狀態,直到戰爭結束一段時間了還是如此。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來到高潮,當時他在第二屆作家代表大會(the Second Writers Congress)上發表演說,這是美國共產黨透過一個外圍組織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Carnegie Hall)所舉辦的。在此,海明威為共產黨所做的事達到了頂點,他認為作家必須反對法西斯主義,因為這是唯一不允許他們說真話的統治方式。他認為知識分子有責任到西班牙去做點事──應該停止爭論書本知識裡的學說論點,開始作戰:「戰爭已開始,將且持續很長的時間,任何想要研究戰爭的作家,都該去打仗。」[43]
……
為什麼海明威渴望死亡?這在作家當中一點也不稀奇。與他同時代的伊夫林.沃(Evelyn Waugh)是地位與他相當的英語作家,也渴望死亡。但是伊夫林.沃不是知識分子:他沒想過要靠自己的智能重新設計人生的規則,而是屈服於教會的傳統教義,在海明威過世五年後自然死亡。海明威建立的規範基於榮譽、真實、忠於自我,但這三者他都搞砸了,而這三者也毀了他,更嚴重的是,他或許覺得他在自己的藝術中是失敗者。海明威有很多嚴重的缺失,但有一樣他並不缺乏──對藝術的真誠,像燈塔般照亮他的全部生命。他為自己設立的任務,是創造新的英語寫作與小說寫作方法,而且他成功了。這是我們語言史中的重要事件,也是現在的英語中無法避免的一部分。他以巨大的創作技巧、精力與耐心,全心投入這項任務。這件事本身就艱難。但正如他所發現的,更艱難的是要維持他為自己設立的諸多創作高標準,這在一九三○年代中期的他身上就清楚可見,並加重了他慣有的憂鬱症。從那時起,他少數成功的作品都只是他長期走下坡的例外。要是海明威少一點藝術家氣息,只是一個普通人,這些事或許對他來說無關痛癢──他大可以單純繼續寫作與出版次級的小說,許多作家都這麼做。但是當他寫得比他最好的小說還差,他會自知,而且無法忍受。他尋求酒精的幫助,甚至連工作時都喝酒。他第一次被看到邊喝邊寫,是在一九二○年代,擺在他面前的是一瓶聖詹姆士金萊姆酒(Rum St James)。這個習慣起初很少出現,然後偶爾出現,再變成恆久不變。到了一九四○年代,據稱他會在凌晨四點半起床,「通常會馬上喝一杯,並站著寫作,一手拿筆,一手拿著酒」。[79] 可以預見這對他工作的影響是悲慘的,一個有經驗的編輯總是能看出作品的哪個部分是在酒精的幫助下創作出來的,無論寫作者多有才華。海明威開始創作出大量無法出版的作品,以及他覺得還不到他自己最低標準的作品。儘管有些還是發表了,但是看起來比較弱,甚至像在拙劣地模仿他之前的作品。有一、兩部作品是例外,尤其是《老人與海》,但這部作品也有自我模仿的成分。整體而言,他後來的作品水準低落,而且還在下降,海明威意識到他無法讓他的天賦再現,更別說發展了,於是加速了憂鬱與飲酒的螺旋。他是被自己的藝術所殺,他的人生包含一個所有知識分子都該學會的教訓:徒有藝術是不夠的。
1 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主張人能超越感覺和理性,直接認識真理。
2 白色獵人(whitehunter)是歐洲或北美專門狩獵大型獵物的專業獵人。
3 孟喬森(Munchausen)是一位以「編造冒險故事」出名的德國男爵。
4「雙分老爹」(PapaDoubles)是以海明威命名的哈瓦納調酒。
第七章 布萊希特:精於打造形象的冷血作家
Bertolt Brecht 1898-1956
「為了讓自己看起來像是工人階級,他每天都要花上幾小時,在指縫中塞灰塵。」 ── 阿多諾,反布萊希特的社會學家
那些想要影響人類的有識之士,長久以來都知道,戲劇是達成此一企圖最有力量的媒介。在一六○一年二月七日,即艾塞克伯爵(the Earl of Essex)跟他的人馬在倫敦發動造反的前一天,他們付錢給莎士比亞的所屬劇團,上演一齣特別的、未經刪改的《理查二世》(RichardII),使得此劇從此被視為顛覆君主制的劇本。耶穌會所帶領的反宗教改革也將戲劇的演出,定位為公教最高傳教機構「萬民福音部」(propaganda fidei)的核心。最早的世俗知識分子也一樣知道舞台的重要性,伏爾泰與盧梭都有寫過劇本──盧梭還警告戲劇有腐敗公共道德的危險性。雨果利用戲劇消滅了最後的波旁王室(Bourbons),拜倫投入大量心力在詩劇,連馬克思都有戲劇作品。然而,如我們所見,易卜生是第一位慎重且有系統地運用戲劇,來實現社會觀念革命的知識分子,而且出奇地成功。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是他天生的繼承者,雖然他們在大部分的層面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劇作家。布萊希特開創出現代精緻的宣傳劇,成功地利用了一種二十世紀的新文化機構:國家補助的大型劇場。在他死後的二十年,即一九六○與七○年代,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作家。
不過,布萊希特生前就是一號神祕人物,某種程度而言到今天也還是。這是他自己與他效忠的共產黨所刻意為之的,在他生前,他效忠這個組織長達三十年,基於許多因素,他想把公眾對他人生的注意力,轉移到他的作品上。共產黨機構也一樣,不願意讓人仔細研究他的出身、背景和生活方式。[1] 因此,儘管主要的輪廓是清晰的,他的自傳還是留有許多空白。他是在一八九八年二月十日,出生於距離慕尼黑六十四公里的奧格斯堡(Augsburg)一座單調、名聲不錯的小鎮。和 共產黨再三堅持的說法相反,他不是農戶出身,他父母兩邊的祖先可追溯到十六世紀,都是中產階級──鄉紳、醫師、教師,以及火車站長與商人。[2] 他的母親是公務員的女兒,父親從事紙業貿易,在奧格斯堡一家造紙廠擔任首席銷售員,後又擔任銷售主任,他的弟弟瓦爾特(Walter)後來進入這一行,成為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Darmstadt Technical University)的造紙教授。布萊希特有心臟病,看起來柔弱,成為了(就像許多其他的重要知識分子)他母親最寵愛的孩子,她發現她無法拒絕他強烈想要的事物。但是,成年後的布萊希特對其家人毫不關心,他幾乎不曾提起父親,也沒有報答母親的愛,他的母親在一九二○年辭世時,他堅持在第二天邀請一群很吵的朋友到家裡來──「我們其餘的人都悲痛到無法說話,」他弟弟回憶道──而且他還在葬禮前一天就招搖地離開小鎮。儘管後來他在非常難得的幾次自責裡,曾批評自己對母親的行為:「我應該被踩死才對。」[3]
……
事實上,他塑造了一種新型的知識分子,就如同盧梭或拜倫當年所做的一樣。布萊希特自己本身就是這種新型知識分子的原型:嚴厲、冷酷、無情,憤世嫉俗、帶點流氓氣又有著運動員的充沛精力。……
……
希特勒的崛起是促使布萊希特更加推廣其政治立場的因素之一。一九二六年,他讀了《資本論》,或至少讀了一部分,因而開始支持共產黨,儘管露絲.費雪(Ruth Fischer)的提供的證據顯示他到一九三○年代才加入共產黨 [9]。露絲.費雪是德國共產黨領導人,也是他一位作曲家朋友艾斯勒(Hanns Eisler)的姐姐。……
……
在此人生觀背後,是在主要知識分子當中常見的一種特質:堅定不移的自私。但是布萊希特是以一套有系統的、冷血無情的方式來追求利己目標,即便以知識分子的標準來看也非常罕見。他接受了關於屈從的可怕邏輯,意思是,如果他向強者鞠躬哈腰,他就能欺壓弱者。終其一生,他對女人的態度都有一種可怕的一致性,他讓這些女人為他的目標做事,成為農家庭院裡的母雞,而他是公雞。他甚至為他的女人們設計了服裝風格,好跟他的風格相襯:長洋裝、深顏色,有點清教徒的樣子。[21] 他似乎在十七歲初試啼聲時就已經大有斬獲,誘姦了一個小他兩歲的女孩。年輕時他鎖定工人階級的女孩子:鄉下人、農夫的女兒,美髮師、女店員。後來是女演員,大約二十幾個。沒有劇團經理人比他更肆無忌憚地利用選角場合了,而且他特別樂見那些家教甚嚴、天主教背景的女孩墮落。我不清楚女人為什麼覺得他有魅力,他的演員女友瑪莉安(Marianne Zoff)說他一直都很髒,她得幫他清洗脖子跟耳朵。查爾斯.勞頓的妻子艾莎(Elsa Lanchester)說他的牙齒是「從黑嘴裡伸出墓碑來」。但他的聲音很細,有如笛聲,音色高亢,顯然會吸引某些人。瑪莉安說,當他唱歌時,他那刺耳的金屬聲音,會讓她的背脊顫抖。她也喜歡他「像蜘蛛那麼瘦」以及「深色鈕狀的眼睛」,「會令人感到刺痛」。布萊希特(在早年)是個殷勤體貼的人,很會親吻女人的手,他堅持不懈,尤其是他那些很難滿足的要求──不光是他的母親發現他提出很多要求,難以抗拒,他的女人們也是。
此外,儘管布萊希特冷酷無情,但顯然看重女人甚於男人。他交給她們重責大任,儘管只是為了奴役她們。他喜歡為每一個人取特別的名字,只有他能這樣喊她們,例如「碧」、「三月」、「髒東西」等,他不介意女人們爭風吃醋、口出惡言、抓傷、爭吵,事實上他喜歡這樣。他的目標和雪萊一樣,是經營一個小型的性關係共同體,而他是其中的主人。但他在雪萊失敗的地方通常會成功,無論何時都擁有兩個以上的女人,跟她們三人行或四人行。一九一九年七月,有個年輕女人為他生下一子,她名叫寶拉(Paula Banholzer),綽號「碧」,他用結婚的曖昧承諾吊她胃口。一九二一年二月,他跟瑪莉安(綽號「三月」)交往,也搞大了她的肚子,她想要留下孩子但他拒絕:「孩子會毀了我所有內心的平靜」。這兩個女人發現了彼此的存在,並終於在慕尼黑的咖啡館裡找到布萊希特,然後要他坐下,在她們當中二選一。他回答:「都要。」然後他向碧提議先娶三月,讓她的孩子成為婚生子,然後再跟她離婚娶碧,讓她的兒子也成為婚生子。三月給他一大段怒氣衝天的訓話,然後憤而離開咖啡館。比較膽小的碧可能也想這麼做,但她只有起身離開而已。布萊希特尾隨她,進了她火車上的小客房求婚,獲得首肯。幾週後他確實結婚了──但不是跟碧,而是跟三月。她失去第一個孩子,但在一九二三年三月生下一女,名叫哈娜(Hanne)。沒幾個月,布萊希特便與另一個女演員海蓮娜有染,他在一九二四年九月搬進她的公寓房間,兩個月後,他們的兒子史特凡出生。他逐漸擄獲其他性關係共同體的成員,包括他忠實的祕書伊莉莎白(Elizabeth Hauptmann),還有另一個女演員,是在《三便士歌劇》中飾演波莉(Polly)的可樂娜(CarolaNeher)。布萊希特與三月在一九二七年離婚,讓他得以再次走入婚姻。這回他會選誰?他猶豫了兩年,最終選上一直對他很有幫助的海蓮娜。他送了束鮮花彌補可樂娜,說:「幫助不大,但我沒別的意思。」她把那束花砸在他頭上。伊莉莎白自殺未果。這一團混亂以及讓女人們受苦的安排,卻讓布萊希特心安理得。對於這些為他受苦受難的女人,他不曾表現過心緒不寧的跡象,一次都沒有。為了達到目的,她們可以被利用然後被拋棄。
有一個悲慘的個案是瑪格麗特(Margarete Steffin),綽號「髒東西」,是一個業餘女演員。他給了她一個角色,然後在排戲期間誘姦她。她跟著他離鄉背井,成為一個不支薪的祕書。她天資高,通曉數種外語,處理他所有的外國通信(布萊希特除了母語,很難應付其他語言)。她患有結核病,在一九三○年代離開本國期間病情逐漸惡化。當她的醫師友人隆德(Dr Robert Lund)催促她去醫院時,布萊希特反對:「那不會有什麼幫助的,她不能住院,因為我需要她。」因此她放棄治療,繼續為他工作,一九四一年他要前往加州時,在莫斯科拋棄她。數週後她在那裡驟逝,死時手裡拿著布萊希特發給她的電報,得年三十三歲。
另一個例子是露絲(Ruth Berlau),是他自一九三三年起的外遇對象,她是聰慧的丹麥人,二十七歲,是布萊希特從她傑出的醫師丈夫那裡偷來的。和其他情婦一樣,他交付她很多的祕書與文學工作,確切來說,他非常留心她對自己劇作的評語。這讓海蓮娜十分生氣,她在布萊希特的女人裡最討厭露絲。露絲和布萊希特在美國時大發牢騷:「我是布萊希特的地下太太」、「我是一個一流作家的娼妓」。她的精神失常越來越嚴重,不得不在紐約的貝爾維尤醫院接受治療。布萊希特對此的評論是:「沒有比瘋狂的共產主義者更瘋的了。」出院後她開始酗酒,跟著布萊希特到東柏林,有時順從,有時當眾吵起架來,直到他終於把她趕回丹麥,之後她因為酒精中毒而病倒。露絲熱心又才華洋溢,她這些年所遭遇的痛苦,光想就很難忍受。
海蓮娜是布萊希特的女人中最堅韌,但也最卑躬屈膝的一個,事實上她取代了他母親的位置。布萊希特和馬克思一樣,有剝削人的長期需求,而在海蓮娜身上,他實現了他的剝削傑作,是馬克思的燕妮與小莉娜的合體。在許多方面,海蓮娜都是個有主見的女人,領導有方,組織能力絕佳。從表面來看他們地位平等、實力相當:他叫她「海蓮娜」,她叫他「布萊希特」。但她缺乏身為女人、尤其是性吸引力的自信,而他抓住這個弱點加以利用。她在家跟在劇場都為他做事,在家裡,她帶著熱情活力洗洗擦擦,搜索古董店裡的好物件,認真地做菜,為他的同事、朋友與女人舉辦永無止盡的派對。她使盡渾身解術加大他的職涯利益,當他在一九四九年獲得自己的劇院時,她為他管理:票房、帳單、布景、清潔、打雜與伙食,所有行政事務。但他清楚、甚至殘酷地表明,她只負責管理這棟大樓,而與創意活動無關,強調她被排除在外。如果她要商討劇院業務時,必須寫信跟他預約時間。
在家裡,他們確實有各自的房間,還有專屬的門鈴,這是布萊希特為了不讓她破壞自己玩女人的最大限度──這在他的柏林歲月裡無情而持續地進行,像是與她無關一樣。當時他的權位,提供了與年輕女演員肢體接觸的機會。海蓮娜偶爾會忍不下去而離家出走。但多半時候她堅強不屈,順從和寬容。有時她會給年輕的情婦忠告:布萊希特是個非常愛吃醋的男人,自己濫交,卻期待他的女人們忠貞以對,或起碼要忠於他的指導。他要求掌控,這代表他要知悉一切,如果情婦不陪他,他可以打好幾通電話確認她做了些什麼。到頭來,他像是一頭老雄鹿,得賣力讓他的雌鹿們冷靜下來。
布萊希特一輩子密集地與女人私通,沒有時間分給孩子。他至少有兩名私生子。露絲在一九四四年生下一子,早逝。還有一個大兒子是寶拉生的法蘭克(Frank Banholzer),他長大成人,卻在一九四三年在俄羅斯前線陣亡。布萊希特沒有像馬克思不承認亨利那樣拒絕承認,但他對兒子也不感興趣,幾乎沒見過他,更不曾在日誌裡提起他。不過他的婚生子在他的生活中出場次數也不多。布萊希特不情願花時間在他們身上,陪伴他們。這是知識分子理想主義的尋常故事,理想比人更重要,「人類」又比男人、女人、妻子、子女重要。演員霍莫爾卡(Oscar Homolka)的妻子佛羅倫絲(Florence)在美國結識布萊希特,對他的結論下得很妙:「在他的人類關係中,他是一位人權鬥士,但不關心跟他周遭許多人幸不幸福。」[22]布萊希特自己則是引述列寧的話,說一個人必須對個體殘忍,才能為集體服務。
……
阿多諾和他的朋友會這麼討厭布萊希特,理由之一,是對於他跟「工人們」的一體感憤恨不平,看出這只是詭計。當然阿多諾等人自稱了解「工人們」真正的所求、所感與信念,也同樣毫無根據──他們也同樣過著全然中產階級的生活,就像馬克思自己,從沒遇過做苦工的人。但起碼他們沒打扮成無產階級,穿著由高價裁縫店精心設計的無產者衣服。這是撒謊,某種程度的計畫性詐欺,這讓他們覺得布萊希特令人噁心。例如,有一則他自己傳開的假故事,說他為了赴約而身著「工裝」來到一間昂貴飯店的門口──發生的地點換來換去,有倫敦薩佛伊飯店(Savoy)、巴黎麗思飯店、紐約廣場飯店(Plaza)──結果卻被穿著制服的守衛攔下。以布萊希特跋扈的本性,要是有人阻止他想做的事,他大可表現得像個被激怒的德國貴族地主階級一樣,這個假故事不太可能發生。但布萊希特利用這件事來象徵自己跟資本主義制度的關係。在這個故事的眾多版本中,有一則是他受邀參加一場奢靡的西方招待會,在入口處被擋下來,並要求他填寫一張表格。當他填完後,看門人問:「布萊希特?你是貝托爾特.布萊希特的親戚嗎?」布萊希特回答「是的,我是他兒子」然後離開,邊走邊喃喃自語:「在每個山洞裡,你都可以找到一個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呢。」[27]
布萊希特某些宣傳手法是從卓別林(Charlie Chaplin)身上學來的,他很推崇卓別林,曾經評價他導演做得比他還好。因此,當他搭乘汽車抵達一場正式宴會,守衛為布萊希特打開車門時,他會故意從另一邊下車,讓守衛看起來很蠢,逗得眾人哄堂大笑。巧的是,那汽車還是一部斯泰爾老車。布萊希特大動作地婉謝了另一部東德公務用大型豪華轎車的特權,但是,開那部斯泰爾(包括燃料、備料、維修等)實際上也是一種特權。在當時,與政權毫無瓜葛的人,不可能開私家車。而且斯泰爾對布萊希特來說還多了一項優勢,能當個人宣傳的象徵。
第八章 羅素:不合邏輯也非理性的哲人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本國最有害的怪人之一。」 ── 尼柯森爵士,英國外交官員
歷史上從沒有知識分子能像第三代羅素伯爵,也就是伯蘭特.羅素(Bertrand Russell)那樣,這麼長期對人類提出建議。他出生於格蘭特將軍(Ulysses S. Grant)再度選上美國總統的那一年,死於水門案發生的前夕。他比小說家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和克萊恩(Stephen Crane)小幾個月,比美國總統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和英國漫畫家畢爾彭(Max Beerbohm)大個幾週。但他活得夠久,久到能向一九六八年的學生抗議浪潮致意,久到能欣賞劇作家史塔帕(Stoppard)與品特(Pinter)的作品。這段時間,他持續針對五花八門到令人瞠目結舌的主題,發表忠告、規勸、報告和警語。他的一份著作列表(肯定是不完整的)列出六十八本書,其中第一本《德國社會民主》(German Social Democracy)發行於一八九六年,當時維多利亞女王還有五年才過世,羅素的遺作《論分析》(Essays in Analysis),是在尼克森總統辭職的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在這段期間,他發表的作品主題包涵幾何學、哲學、數學、司法制度、社會重構、政治理念、神祕主義、理則學、布爾什維克主義、中國問題、大腦學、工業、原子入門(這在一九二三年出版,三十六年後他出了一本探論核武的書)、科學、相對論、教育、懷疑主義、婚姻、幸福、倫理、失業、宗教、國際事務、歷史、權力、真理、知識、權威、公民權、道德、傳記、無神論、智慧、未來、裁減軍備、和平、戰爭犯罪等等。[1] 這還沒算上報章雜誌大量的文章產出,幾乎囊括所有能想得到的主題,例如「唇膏使用法」、「觀光客的禮節」、「挑雪茄」與「揍老婆」等等。
為什麼羅素覺得自己夠格給別人那麼多忠告?為什麼大家都會聽他的?第一個問題的答案,乍看之下並不明顯,或許他之所以寫了那麼多,最大的理由是因為他發現寫作非常容易,而他拿到的稿酬又那麼豐厚。他的友人馬勒森(Miles Malleson)在一九二○年代曾經這樣寫他:「每天早晨,羅素會獨自散步一小時,構思當天要寫的內容。然後他便返家,用剩下的晨光來寫作,順利、輕鬆地寫,沒有一處需要修改。」[2] 他把這項宜人活動的財務結果記錄在一本小本子上,列出他畢生透過刊登或廣播所收到的稿費。他把小本子在放在外套內袋,在他極少數懶散、喪氣的時刻,便拿出來細細品味,他稱之為「最有益的消遣」。[3]
……
怪的是,羅素很會識破──與公開譴責──別人身上這種和他一樣的危險組合:理論上知道,但在實務上卻看不見他人如何感受,也不知道他們想要什麼。一九二○年,他造訪布爾什維克黨人主政的俄羅斯,並於五月十九日與列寧會面。他發現他是「一個具有形體的理論」,他寫道:「他給我的印象是鄙視平民,是一個知識分子貴族。」羅素看得很透徹,這樣的組合不具有英明統治的能力。確切來說,他補充:「如果我是在不知道他是誰的情況下遇見(列寧),我應該不會認為他是一個偉人,反而會猜他是個堅持己見的教授。」[17] 他無法或不願知道的是,他對列寧的描述,某種程度上套用在他身上也是可以。他也是個知識分子貴族,鄙視人民,偶爾憐憫人民。
……
…… 但即便要付出這樣的代價,戰爭還是值得的。必須徹底消滅共產黨,必須建立世界政府。」[25] 羅素不斷強調非快不可:「俄羅斯人遲早會擁有原子彈,一旦他們也有,就更難對付了。每件事都要用最快的速度加快進行。」[26] 即便俄羅斯已經爆破了一枚原子彈,他還是繼續彈他的老調,強烈主張西方必須發展氫彈。「以現在的世界趨勢,我不認為限制原子衝突的協議除了危害還有什麼用處,因為每一方都認為另一方會規避協議。」然後,他以堅不退讓的形式提出「死亡都比赤化好」的主張:「如果發生下一場戰爭,那將是降臨在人類身上最慘烈的戰爭。我唯一想到的更慘烈的災難是:克里姆林宮的權力擴張到全世界。」[27]
羅素倡導的「預防性戰爭」概念廣為人知,並在這些年間受到廣泛討論。一九四八年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國際哲學大會,他被蘇聯代表團團員阿諾斯特.柯爾曼(Arnost Kolman)猛烈攻擊,他以相同的粗暴方式回擊:「回去告訴你克里姆林宮的主子,他們得派出更能幹的手下,才能完成他們宣傳與騙人的政黨綱領。」[28] 遲至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他還在向《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投書:「雖然一場新的世界大戰非常可怕,但對我來說,還是好過一個世界共產帝國。」
然而,大約就在此時,羅素的看法突然徹底改變。就在隔月,一九五三年十月,他在《國家》(Nation)雜誌中否認他曾經「支持對俄羅斯發動預防性的戰爭」。他寫道:「這整件事都是共產黨人編派的。」[29] 據一位朋友記載,有好一陣子,只要有人拿出他的戰後觀點給他看,他就宣稱:「不可能。那是共產黨記者杜撰的。」[30] 一九五九年三月,他接受了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電視訪問,在弗里曼(John Freeman)知名的「面對面」(Face to Face)節目裡,羅素改變了風向。美國的軍備裁減專家們寄來了羅素之前說法的篇章與詩文,讓他再也抵賴不了,所以他告訴質疑他預防性戰爭路線的弗里曼:「這全是事實,而且我並不後悔。這跟我現在的想法完全一致。」[31] 隨後,他投書給英國廣播公司的週刊《傾聽者》(The Listener)說:「事實上,要不是一九五八年柯伯格(Alfred Kohlberg)先生與馬賽博士,帶來我在一九四七年的評論文章裡說過的話,我根本就忘了我曾想出一個這麼挑起戰端的威嚇政策。我讀到時瞠目結舌。我無可推託。」[32] 在他一九六八年的自傳第三卷,他大膽地進一步解釋:「…… 我當時給出建議,是無意間給的,沒有真的希望它被採用,因此早就忘了。」他補充:「我是在私人信件裡提到的,然後在一場演說中又提到,不知道媒體會當一回事詳細研究。」[33] 但是克拉克的調查顯示,羅素在許多文章與演說中,一再地為預防性戰爭據理力爭,而且歷時多年。很難相信他會對堅持這麼久、又公開表明的觀點,忘得一乾二淨。
當羅素告訴主持人弗里曼,他一九五○年代晚期的核武觀點,與他戰後的觀點一致,都是支持預防性戰爭時,他是在以另一種曲解事實的方式,讓他人輕信。確實,大部分人會說他在胡扯,但這當中有某種一致性:極端主義的一致性。羅素提出的預防性戰爭與「死亡都比赤化好」,都是運用無情與不顧人道的「邏輯」,將辯證的理智推向極端的例子。這確實是羅素的弱點。他的邏輯指令伴隨的是謬誤的價值觀,以此指點人類該如何處理事務,認可這種邏輯觀點甚至比普通的本能欲望更重要。
……
真的必須要說,羅素一生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持續不停的爭論,而不是一位格言家。他的名言錄,讀起來未必勝過托爾斯泰,「所謂紳士是指其祖父年收入不超過一千英鎊的人」、「在非洲,民主政體絕對行不通」、「小孩必須送去寄宿學校,讓他們遠離母愛」。他形容美國的母親們「其過失是天生失能,其情感的泉源似乎已經枯竭」,還有「幾乎很難從女人身上學到對生活的科學態度」。[52]
上面的最後一句評論提醒了我們,儘管羅素生命的最後數十年中,他幾乎只與政治聲明聯繫在一起,但他曾經因為談論兩次大戰相關之事而變得更加聲名狼藉,諸如「試婚」、自由戀愛、離婚制度改革與男女同校等等。至少在理論上,他是支持婦權倡議者所闡述的信條的,他要求婦女在婚姻內外都一樣平等,並將她們描繪成過時的道德體系下的受害者,這種道德體系沒有真實的倫理基礎。性解放應該受到欣賞,他嚴厲批評過去傳統被視為「婦德」的禁忌與犧牲;[53] 他對女人、社交生活、孩童與人際關係的看法,有許多附和雪萊之處。他的確特別熱愛雪萊,宣稱雪萊的詩把他對人生的態度表達得最淋漓痛快。他在威爾斯的落腳處,是雪萊在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一三年時,嘗試在當地建立社區之處,他位於波斯馬多格(Portmadoc)海口的寓所彭林城堡(Pias Penrhyn),跟雪萊友人梅鐸斯(Maddox)的房子,是出於同一位建築師的作品。
然而,和雪萊一樣,他對女人的實際舉止,跟理論上的原則並不始終一致。他第一個太太愛麗絲,是個有教養、忠誠、心胸寬厚的美國貴格派教徒,但就像雪萊的海莉兒一樣,因為丈夫越來越放蕩而受苦。就如我們前面提到的,羅素在年齡二十歲開頭以前家教甚嚴,對性也拘謹保守。確實,在一九○○年,當羅素的哥哥、身為第二代伯爵的法蘭克(Frank)離開妻子,隨隨便便離婚又再婚的時候,他就拒絕承認新嫂嫂,然後建議法蘭克,用餐時不要讓她上桌(法蘭克後來在上議院的法庭被控重婚罪)。但隨著羅素年紀漸長,他變得像雨果一樣,更好色也更傾向於不遵守社會規則,除非他發現遵守規則對他來說比較省事。
愛麗絲正式被拋棄,是在十六年後的一九一一年三月十九日,那一天羅素到貝德福廣場四十四號,造訪活潑的布魯姆斯伯里(Bloomsbury)交際花奧特琳.莫雷爾夫人(Lady Ottoline Morrell)。他意外發現她丈夫菲利普不在,便和她發生了關係。在他的說法裡,他說那一夜與她並未「正式定下關係」,但已決意要「離開愛麗絲,並讓奧特琳離開菲利普」。莫雷爾太太或許「對此事毫不在意」,羅素卻很篤定她丈夫「會殺了我們倆」,但他「願意為那一夜春宵付出代價」。羅素馬上把消息告訴愛麗絲,她暴怒,要求離婚,並把奧特琳牽扯進來。經過一番爭執後,羅素「堅決地」說,如果她真的做了她揚言要做的事,「我應該自殺來阻止她。」隨即,「她的怒火變得難以忍受。在她發飆幾小時後,我給她姪女講了一堂洛克的哲學」。[54]
……
至於邏輯,也是需要時才會訴諸使用。在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時,羅素和許多作家一起被勸進簽署一份抗議信。我曾負責去談讓這封信刊登在《時代雜誌》上,要是按照慣例,以字母來決定署名順序,這封信將題為「來自艾米斯(Kingsley Amis)等人簽名」。而我決定、《時代雜誌》編輯也同意,如果標題是「來自榮獲功績勳章的羅素伯爵等人」可能會在共產世界裡造成更大的影響,所以我們就這麼做了。但是羅素注意到這個小詭計,而且生氣了,他打電話抗議,並最終連絡上人在印刷廠的我,我當時正在檢查《新政治家》。他說我的蓄意作為會讓人以為他是這封信的發起人。我否認,並說唯一目的是讓這封信的效果放到最大。我說:「畢竟,既然你同意在信上簽名,就不能抱怨被放在首位──這不合邏輯。」羅素憤怒回答「聽你合邏輯的瞎扯!」然後砰一聲掛了電話。
1 該考試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難的數學考試。
2 指如果因為良心、道德或宗教信念,不允許某人遵守某一法律,則他可以不遵守。
3 狄奧根尼(Diogenes)是古希臘哲學家,相傳他住在一個木桶裡,所有財產只包括這個木桶、一件斗篷、一支棍子和一個麵包袋。
4 愛爾蘭傳說中預報死訊的女妖。
5 這兩人為義大利裔無政府主義者,遭美國政府判處死刑,此案曾引起世界公憤,輿論認為判決是出於政治偏見。
6「小亞波羅先生」(MrApollinax)是艾略特一首詩的名稱。
第九章 沙特:哲學大師,以及沙文主義的原型
Jean-Paul Sartre 1905-1980
「我每一個理論,都是征服與占有的行動。我想有一天,在這些理論的幫助下,我會征 服世界…… 最重要的是,我渴望主張占有女人的自由。」 ── 沙特
尚 — 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和羅素一樣,也是個想對大眾諄諄教誨的專業哲學家。但是兩人在手段上有個重要差別。羅素視哲學為平民不能參與的神職學科,一個像他這樣最通俗的哲學家,能夠做的,是提取少量智慧、大幅稀釋,再透過報紙文章、通俗書籍和廣播散布出去。反之,沙特的工作讓他在高中就能教哲學、在咖啡館裡就能議論哲學的,因此他相信透過劇作與小說,能吸引大眾參與他的思想體系。至少有一段時間看起來,他是辦到了。很明顯地,本世紀沒有一位哲學家能像沙特一樣,對世界上這麼多人的心靈與態度(尤其是年輕人)有如此直接的影響。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在一九四○年代末與五○年代是哲學中的顯學。沙特的劇作風行一時,他的著作銷量驚人,有些作品光在法國就賣掉超過兩百萬冊。[1] 他提供了一種生活方式,像是主持著一個世俗的教會,雖然這個教會的概念很模糊。只是到頭來,這一切到底是什麼?
和大部分重要知識分子一樣,沙特是個極度自我的人。考量到他的童年環境,這也不會太過意外。他是典型被寵壞的獨生子。……
……
對沙特來說,一九三○年代是失落的十年。他所期待且熱切渴望的文學名聲沒找上他。大部分時間他都在勒哈佛爾(LeHavre)教書,成為打扮過時的鄉下人縮影。他去了柏林幾趟,在阿宏的建議下,研究起胡賽爾(Husserl)、海德格(Heidegger)與當時歐洲首創的哲學「現象學」。但大部分時間他都在做繁複無聊的教書匠。他討厭資產階級,也確實非常有階級意識,但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事實上,他沒讀過馬克思,至多讀過摘文。他肯定是個叛逆的人,但是他的叛逆沒有動機,他沒有加入政黨。對希特勒的崛起不感興趣,對西班牙也無動於衷。無論他後來對外怎麼宣稱,記錄顯示戰前他沒有強烈的政治主張。……
……
但如果沙特是國王,王后是誰呢?而若他是數萬青年的精神領袖,他又在哪裡領導他們?這是兩個獨立、但其實相關的問題,需要依序檢視。到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冬天,他已經成為歐洲名人,也已經跟波娃交往二十年了。波娃是蒙帕納斯女孩,出生在馳名的圓亭咖啡館(Café de la Rotonde)的樓上公寓。她童年過得很苦,家庭被不名譽的破產擊垮,祖父入監服刑,母親的嫁妝再也拿不回來,而父親是個沒用的花花公子,連個正經工作都找不到。[26] 她苦澀地寫到雙親:「我父親相信德雷弗有罪,而我母親相信亞威存在。」[27] 她以課業為庇護,成為一個女學者,而且是相當一流的學者。在巴黎大學,她是優異的哲學學生。沙特對她感興趣,把她帶進自己的圈子裡,並告訴她:「從現在起,由我來庇護妳。」某種程度而言,這依然是事實,儘管對她來說,兩人的關係是憂喜參半。她比沙特高三公分,年紀小三歲,而且,就嚴格的學術意義來說,能力也比他強。有個跟她同年代的人,鞏迪雅克(Mauricede Gandillac)形容她的作品「精確、苛求、細緻,非常專業」。儘管她年輕,但在哲學學位考上,她幾乎是一開始就打敗沙特,考官喬治.戴維(Georges Davy)與尚.瓦爾(Jean Wahl)都認為她是更好的哲學家。[28] 她和沙特一樣,也是個引人入勝的作家,在許多方面寫得比沙特好。她寫不了劇本,但她的自傳,儘管事實一樣不可靠,卻比沙特的自傳有趣多了。而她的一流小說《名士風流》(Les Mandarins)描寫戰後法國的文學世界,贏得了龔古爾文學獎,也比沙特的任何小說好太多了。此外,除了說謊,她不具備沙特的任何缺點。
但這位才華洋溢又有主見的女人,還是成了沙特的奴隸。幾乎是從他們初次見面,她的成年生活就被占滿了,直到他過世為止。她擔任他的情婦、代理妻子、廚師跟經理,女保鏢與護士,卻在他的一生當中,沒有任何一刻獲得合法或財務上的地位。就一切本質而言,沙特對她並沒有比盧梭對泰蕾茲更好。實際上更糟,因為沙特花名在外。文學史上,男人剝削女人到這麼糟糕的案例很少見。而沙特更特別,因為波娃是終身的女權主義者。一九四九年,她寫出了現代女權主義的第一部宣言,《第二性》(La Deuxième sexe),在全世界都極為暢銷。[29] 開篇便說「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而是後天塑造的」,這是刻意回應盧梭《社會契約論》的開頭。事實上,波娃是女權運動的先驅,也理當是女權運動最初的領導者。但她自己的人生,卻每一件事都背叛了她自己的主張。
沙特究竟是如何建立並維持對波娃的支配地位的,並不清楚。她無法誠實地寫出他們的關係,他則是從沒煩惱過要對他們的關係寫些什麼。初次見面時,他書讀得比她好,能摘出精華滔滔不絕,她覺得極具魅力,難以抗拒。他對她的控制顯然是知識分子的那一種,不會是情欲的掌控。她大概在一九三○年代成為他的情婦,但在某些階段結束關係。一九四○年代,他們的性關係似乎已經近乎不存在,只有當沙特找不到更好的對象時,她是永遠的備胎。
沙特是一九六○年代所謂的「男性沙文主義」的原型,想在成年生活裡重新創造兒時的「天堂」,他總是在香閨裡,被一群愛慕的女人環繞。他是從勝利與占領的角度來思考女人,他在《嘔吐》裡說:「我每一個理論,都是征服與占有的行動。我想有一天,在這些理論的幫助下,我會征服世界。」他寫道,他想要自己完全自由,並且「最重要的是,我渴望主張占有女人的自由」。[30] 他和許多老練的誘姦者不一樣,他並不討厭女人。他確實對女人比對男人更有好感,或是許因為她們比較不會刻意跟他爭論。他提到:「比起跟阿宏討論哲學,我更喜歡跟女人聊瑣事。」[31] 他喜歡寫信給女人,有時一天寫十幾封。不過女人對他來說不是人,而是戰利品,能繫在他的半人馬腰帶上,而他企圖以偽善的面紗,試著捍衛與合理化他的征服手段。例如他說他需要「征服女人猶如征服野生動物」,但是「這麼做只是為了改變她未被馴服的狀態,好讓她跟男人一樣平等」。或是再一次,回顧他早期的誘姦成果,他的省思是「皆有帝國主義統治的色彩在裡頭」。[32] 但沒有證據顯示這樣的想法使他偏離了潛在的獵物。他只是說給別人聽的。
……
沙特跟才智相當的任何人都無法維持友誼的情形,這解釋了他的政治觀點前後矛盾、不著邊際,偶爾十分輕浮的現象。實情是,他不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他在四十歲前對於邏輯上的「必然結果」沒有看法。在他跟柯斯勒與阿宏(兩位的判斷力都在一九四○年代晚期變得成熟,成為政治要人)分道揚鑣後,立場搖擺不定。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間,他意識到自己在年輕人中極具威望,於是感到緊張,不知道要支持哪個政黨。看起來他似乎認為,身為知識分子,有種必須支持「工人」的道德責任。問題出在沙特並不認識、也沒有花心思去會見任何工人,除了他那優秀的祕書尚.庫是無產階級出身,保留濃厚的奧德省(Aude)口音,勉強還算是一個。那麼,是否該支持最多 工人支持的政黨呢?在一九四○年代的法國,這表示要支持共產黨,但是沙特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確切來說,馬克思主義跟他所鼓吹的強烈個人主義的哲學完全對立。雖是這樣,他還是無法譴責共產黨或史達林主義──這是他跟阿宏與柯斯勒起爭執的原因之一。他以前的學生尚.卡納帕(Jean Kanapa)如今是共產黨最重要的知識分子,厭惡地寫道:「他是個喜歡跟馬克思主義調情的危險動物──因為他沒讀過馬克思,儘管他或多或少知道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內涵。」[47]
……
一九五二年,沙特解決了他對共產黨的兩難,決定支持共產黨。這是在經歷兩次共產黨鼓動宣傳的活動後,而做成的非理性判斷:分別是「亨利.馬丁事件」8,以及由共產黨策畫的無情鎮壓暴亂,後者是為了對抗美籍的北約指揮官李奇威(General Matthew Ridgeway)。[51] 一如當時許多人預見的,共產黨發起釋放馬丁的運動實際上導致當局把他關得比原本更久,而共產黨並不在乎,他被監禁正符合他們的目的。但只是沙特應該要更有判斷力才對,他的政治眼光從他譴責守舊的總理皮奈(Antoine Pinay)建立獨裁政權時就能看出端倪。[52] 沙特從未顯示他真的懂、或是對議會民主感興趣,更別說是懷抱熱情了。在多黨制的社會投票表決,根本不是他所定義的自由。那他指的自由是什麼?這問題就更難回答了。
沙特在一九五二年與共產黨人密切合作,完全沒道理。此時西方以文件證明並承認史達林的可怕罪行,其餘左翼知識分子也正成群地離開共產黨。沙特發現自己左右為難。他觀察到自己對史達林陣營心神不寧地緘默,而他為自己的緘默所辯護的論點,卻跟他在《摩登時代》所承諾的宣言完全抵觸。他無力地主張:「由於我們不是該黨黨員或公開的支持者,我們沒有書寫蘇聯勞改營的責任。只要沒有發生對社會學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我們有自由不關心該體制本質之爭論。」[53] 他也逼自己對布拉格斯蘭斯基(Slánský)和其他對捷克猶太裔共產黨人駭人的審判保持緘默。更糟的是,他讓自己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共產黨人的世界和平運動(Communist World Peace Movement)在維也納舉行的荒唐大會裡,被當成淪為一隻表演把戲的熊。沙特這是在抱法帝耶夫(叫沙特鬣狗與豺狼的那位)的大腿,他告訴會議代表他畢生最重要的三件事,是一九三六年的人民陣線、法國解放運動,與「這次大會」──這是公然說謊,尤其是在共產黨大頭的一聲令下,他終止了他的反共舊劇作《骯髒的手》(Les Mains sales)在維也納的演出。[54]
在沙特持續支持共產黨路線的這四年期間,他的某些言行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他就像羅素一樣,讓人想起笛卡爾名言中令人不快的真理:「沒有什麼荒謬不可信的東西,是不曾被哲學家擁護過的。」一九五四年七月,在造訪俄羅斯後,他接受了同情共產黨的《解放報》(Libération)記者兩小時的訪談。這是自一九三○年代初期蕭伯納惡名昭彰的考察隊以來,重量級的西方知識分子對蘇聯最卑躬屈膝的說法了。[55] 他說蘇聯治下的公民之所以不出國,不是因為被限制,而是因為他們沒有離開他們超棒國家的欲望。他主張:「比起來,蘇維埃公民對政府批評得更多,也更有效。」確切來說,他主張:「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裡,有評論的完整自由。」多年後,他坦承他說謊:
我一九五四年第一次造訪蘇聯,我說了謊。實際上,說謊可能是太過強烈的說法:我是寫了篇文章…… 說了些蘇聯的好話,但我並不相信。我這麼做,部分原因是一回國就詆毀款待你的東道主,我覺得不太禮貌,部分原因是我真的不知道在蘇聯跟我的理念之間,我該抱持什麼立場。[56]
這是來自「數萬青年的精神領袖」的奇怪告白,此外,它就跟他原本的謊話一樣是騙人的,因為當時沙特很清醒,並且是蓄意讓自己跟共產黨站在同一陣線。事實上,對他在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的某些言行避而不提,是更仁慈的做法。到一九五六年時,沙特在法國與世界的聲譽已經非常低落,低到他不可能沒有感受。他以攻擊蘇聯入侵匈牙利來替自己解圍,作為跟莫斯科和共產黨決裂的理由,或至少是個藉口。同時,他對迅速發展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Algerian War)產生興趣──尤其是一九五八年後,戴高樂再度執政,提供了一個現成的討人厭的人物──為他贏回了在獨立派左翼中的聲譽,尤其是年輕人。某種程度而言,這個策略是真誠的,在有限的程度上也是成功的。沙特體驗到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美好」,一如他體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美好」,和羅素不同的是,雖然他很努力,卻沒有成功被逮捕過。一九六○年九月,他說服了大約一百二十一名知識分子連署一份聲明,主張「(公務員與軍隊等)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有權抗命」,第四共和政府差一點就把他關進牢裡了。但第五共和政府比較老練,是由兩位在知識與文化上的傑出人士,戴高樂自己和馬爾羅所主宰。馬爾羅說:「最好讓沙特在協和廣場(Placedela Concorde)大叫『恐怖分子萬歲!』然後再逮捕他,讓我們自己為難尷尬。」戴高樂以維永、伏爾泰與羅曼.羅蘭為例,告訴內閣說最好別動知識分子:「這些人在紅極一時的時候帶來很多麻煩,只要與我們的法律、國家的團結不相衝突,我們必須繼續尊重思想與言論的自由。」[57]
一九六○年代,沙特大部分時間都在遊歷中國與「第三世界」,這是一九五二年地理學家索維(Alfred Sauvy)發明的用語,但將之普及的卻是沙特。他和波娃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經常能看到他們與非亞獨裁者談天的留影──他穿著他第一世界的西裝與襯衫,她則穿著她女教師的羊毛衫,搭配吸睛的「民族風」裙子與圍巾。對於邀請沙特的那些政權來說,他發表的談話比較能夠接受,至少沒有比他對史達林執政的俄羅斯的讚譽更誇張。他說卡斯楚:「從古巴革命中誕生的國家,是直接民主。」說狄托(Tito)執政的南斯拉夫:「實現了我的哲學。」說納塞執政的埃及:「過去我一直拒絕談論社會主義跟埃及政權的關係。現在我知道錯了。」他對毛澤東主政的中國特別熱情,他喧鬧地譴責美國在越南的「戰爭罪行」,將美國比作德國納粹黨(但他又拿戴高樂來跟納粹比,忘了巴黎淪陷期間,他自己的劇作登台上演時,這位將軍正在對抗納粹)。他跟波娃一直都反美:一九四七年,在訪美之後,波娃在《摩登時代》寫下荒謬的報導,充滿了可笑的拼字錯誤,比如「格林尼威治村」(Greeniwich Village/Greenwich Village)、「馬克思.吐溫」(Max Twain/Mark Twain)、「詹姆斯.艾利吉」(James Algee/James Agee)和瘋瘋癲癲的斷言,例如只有有錢人才獲准進入第五大道的商店。幾乎所有說法都不是真的,因此成為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絕妙辯論的笑柄。[58] 如今到了一九六○年代,沙特在羅素名譽掃地的越南戰爭罪法庭(於斯德哥爾摩舉行)扮演重要角色。這些不太有意義的活動,對世界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只是讓沙特不管對嚴肅話題發表什麼談話時,影響力都大受打擊。
儘管如此,沙特對第三世界的仰慕者提出的建言,還是有更邪惡的一面。雖然沙特不是行動派──這是卡繆更傷人的嘲笑之一,說沙特「嘗試在脫離現實的情況下創造歷史」──但是他一直都鼓勵別人採取行動,而所謂的行動是指暴力。他成為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的資助者,法農是一位非洲的思想家,或許能稱為現代黑色非洲種族主義的奠基者。沙特為法農宣揚的暴力宣傳書《大地上的受苦者》(Les Damnés de la terre)作了一篇甚至比正文更嗜血的序。沙特寫道,對一個黑人來說,「射殺一個歐洲人是一石二鳥,讓一個壓迫者被摧毀,同時又消滅了被壓迫者」。這是更合乎時代需求的存在主義:透過謀殺來自我解放。正是沙特發明了確認既存秩序是否「暴力」的文字技巧(擷取自德國哲學),例如「制度化的暴力」,這樣就有了正當理由可以為了推翻這種暴力而殺人。他主張:「對我來說,根本問題是,要否決左翼不該以暴制暴的理論。」[59] 注意:他說的不是「一個」問題而是「根本」問題。由於沙特的文章廣為流傳,在年輕人的圈子裡尤其如此,他因此成為許多恐怖主義運動的學術教父,從一九六○年代晚期以來,這些運動便開始壓迫社會。他沒有預見到,他從哲學上激勵的大部分黑人暴力活動,並未用來反抗白人,而是去打擊其他黑人,但這是作為一個有智慧的人應該要預見的。扶植法農來煽動非洲,讓非洲局勢益發惡化,他促成了席捲非洲大陸大部分地區、從一九六○年代至今的內戰與大屠殺,對越戰即將結束的東南亞危害更甚。柬埔寨從一九七五年四月起發生駭人的紅色高棉大屠殺,死亡人數介於總人口數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是由一群名為「最高組織」(Angka Leu)、說法語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所籌謀的,該組織一共有八位領袖,包括五名教師、一位大學教授、一位公務員,還有一位經濟學家。他們一九五○年代都在法國留學,不但都加入共產黨,還吸收了沙特哲學中行動主義與「必要暴力」的信條。這些大屠殺是他思想的產物。
在沙特人生最後的十五年,其行動沒有多少意義。他有點像羅素,拚命維持著先鋒的地位,一九六八年,他表明立場支持學生,一如他從儅教師的第一天起就這麼做。在一九六八年五月的諸多事件中 9,很少人因為有功而崛起──阿宏是法國傑出的例外 [60]──因此沙特的有失尊嚴的表現或許不值得特別責難。在一場盧森堡廣播電台的訪談中,他向學生設置的街壘致敬:「暴力是學生們加入父權體制之前,唯一不被改變的事物…… 目前,我們軟弱的西方國家唯一反對國家統治集團的力量,便是以學生為代表…… 這取決於學生認定他們該如何建立他們的作戰模式。我們甚至無法針對此議題,為他們提供建議。」[61] 這一個花了三十年光陰給年輕人建議的人,說出了這種老套的說法。還有更昏庸的說法,他告訴學生:「你的行動最令人關注之處,就是它驅動想像力快速前進。」波娃也一樣滿腔熱血,她熱情地說,學生在巴黎大學牆上塗鴉的「大膽」標語之中,她最感動的是「禁止是被禁止的」。沙特屈尊地訪問只做了一天學生領袖的龔 — 本第(Daniel Cohn-Bendit),並在《新觀察家》(Nouvel-Observate)雜誌寫了兩篇文章。他覺得這些學生「百分之百正確」,因為他們要摧毀的政權是「懦弱的政治…… 必須要扼殺」。其中一篇文章大部分是在攻擊他之前的朋友阿宏,而阿宏幾乎是當時一堆愚蠢行為中唯一保持清醒的人。[62]
但是這些滑稽的動作並不出自沙特的內心,是他的年輕奉承者們敦促他動起來。當五月二十日他現身巴黎大學的圓形露天劇場,向學生發表演說時,他看起來像是一位困惑的老人,因為四周都是明亮的燈光、煙霧,以及「尚 — 保羅」的呼聲 ── 他的助手們絕不敢這樣直呼其名。他的發言不太好懂,結尾時說:「我要離開你們了。再不走,我最後會說出一大堆蠢話。」一九六九年二月十日是他最後一次出現在學生面前,他慌張地被攙扶著,就在開始演講前,有人唸了一 張學生領袖寫的無禮紙條給他聽:「沙特,要清楚,要簡潔。我們還有很多規章、討論跟通過。」這不是他過去習慣接受、或是能夠遵守的建議。[63]
不過這回他已有了新的愛好。和托爾斯泰與羅素一樣,沙特的專注力很短暫。他對學生革命的興趣維持不到一年。同樣短暫但不尋常的是,他緊接著企圖使自己與「工人們」成為一體,他為這群不可思議但被理想化的存在寫了那麼多文章,卻始終不理解他們。一九七○ 年春天,法國的極左派企圖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歐洲化,這是遲來的嘗試,該運動被稱為無產階級左翼(Proletarian Left),而沙特同意共襄盛舉,名義上他成為其刊物《人民事業報》(La Cause du peuple)的總編 輯,但這主要是為了避免被警察查封。該運動的目標非常暴力,甚至超過沙特的口味 ── 呼籲把工廠經理送進監牢,把議會代表私刑處死 ── 但實際上是原始的浪漫精神、幼稚與強烈的反智。沙特在裡面實無容身之處,他自己似乎也感受到了,抱怨說:「我若繼續跟激進分子混在一起,總有一天會被人推著輪椅擺布,擋到每個人的去路。」 但是他被一群年輕的追隨者簇擁,到頭來還是抗拒不了政治表演的誘惑。於是巴黎把他視為奇觀,這位六十七歲、就連戴高樂(沙特討厭 他)都尊稱一聲「親愛的大師」的沙特,在街頭叫賣品質低落的報紙,在無聊的分流道旁印傳單。有一位攝影師捕捉到他在香榭麗舍大道的身影,那是一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他一身嶄新的無產階級裝束,白色運動衫,厚夾克與鬆垮垮的褲子。他甚至計畫讓自己被逮捕,但不到一小時就被釋放了。十月,他再度現身街頭,在比揚古 (Billaincourt)的雷諾車廠外,站在汽油桶上對著汽車工人滔滔不絕。 《震旦報》(L’Aurore)一篇報導譏諷道:「工人們聽不懂。沙特的觀眾 根本沒幾個,全是他自己帶去的毛澤東主義者。」[64] 十八個月後,他 又去了另一家雷諾車廠,這回他偷偷進入工廠內部,並口頭支持絕食抗議;但保全人員找到他,把他趕了出去。沙特的努力沒有勾起實際車廠工人們半點的興趣。一如既往,他結交的全是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
沙特確實跟羅素一樣,對公共政策的看法沒有任何類型的連貫與一致,沒有任何主義在他死後繼續生存。結果跟羅素一樣,到頭來他所擁護的,不過是屬於左派與青年陣營的成員,那種模糊的渴望罷了。身為一個知識分子,沙特畢竟曾以一種突出的生活哲學(儘管亂七八糟)受到認同,雖然令人不滿意,但總有一大批受過教育的公眾,需要知識分子領袖。盧梭雖然罪大惡極,死後還是廣受尊敬,而沙特是另一頭「聖獸」,在巴黎也由知識分子們籌辦了隆重的葬禮,超過五萬人跟著他的棺柩進入蒙帕納斯公墓,大部分是年輕人。為了能看清楚一點,有些人爬到樹上。其中一人摔下來撞在棺材上。是什麼原因讓他們來參加葬禮?這一大群人出席葬禮,想要擁護的是什麼信念?是跟人性相關、有見地的真理嗎?我們會想好好問一問。
1 小說主角象徵了當時社會中的年輕人,在戰後世界新見解和舊思想中掙扎沉浮。
2 巴黎的聖日爾曼德佩區(St-Germaindes-Prés)在一九四○至五○年代是存在主義運動重 鎮,海明威、畢卡索也是常客。
3 巴黎公社曾短暫統治巴黎並宣布要接管全法國,由於他們殺了兩名法國將軍,加上拒絕 接受法國當局管理,造成「血腥一週」的鎮壓。
4 卡拉斯曾被控謀殺兒子而求處死刑。後來伏爾泰為他辯護,讓他成功洗清罪名。
5 德雷弗是法國軍官,曾被控叛國而終身監禁,後來得到平反。
6 查內托(Zanetto)是歌劇中四處遊蕩、與美麗妓女戀愛的吟遊詩人。
7 路易十四一生情婦眾多,共有十六名私生子女,一六八三年與曼特農夫人(Madame de Mainteno)祕密結婚。
8 亨利.馬丁(Henri Martin)是海軍士兵,因拒絕參與中印戰爭而入獄。
第十章 威爾森:迷失在太平盛世的懺悔者
Edmund Wilson 1895-1972
「馬克思主義是知識分子的精神鴉片。」 ── 威爾森
艾德蒙.威爾森(Edmund Wilson)的例子很有啟發性,因為他讓我們 得以釐清傳統文人與我們所探討的知識分子之間的差異。事實上,威爾森的職涯可說是始於文人,接著變成尋找救世方案的知識分子,然後是 ── 變成一個更憂傷、更有智慧的人 ── 回到他年輕的時候,專注於他真正的專長:文學。他出生時,美國文人已經是個牢固而悠久的團體,確切來說,他們在亨利・詹姆斯身上找到了傑出的模範,對詹姆斯來說,文學是生命,他鄙棄世俗知識分子那種光憑理念就能變出魔法,轉化這個世界與人性的念頭。對他來說,歷史、傳統思想、 秩序與既定的形式,構成了文明的傳承智慧,以及人類行為唯一可靠的指引。詹姆斯對公共事務有著嚴肅的、客觀超然的興趣;他在一九 一五年放棄英國公民資格,以從事自己認為正確的理想事業,這個動作顯示,他認為藝術家應該在重大議題上挺身而出。但文學總是位居第一,那些為文學獻上生命的人 ── 守護祭壇的祭司們 ── 絕不應該為了追求政治上的虛妄眾神而獻身。
……
對於世界的一般事務缺乏平衡處裡的心態,是在知識分子中常見的情況,而我們也屢屢看見像威爾森這樣的文人,在離開知識分子的隊伍後,依然有著這樣的問題。這在威爾森與美國國稅局官員的憤怒交戰後突然且災難性地出現,為此他寫了本憤慨的書。他的問題很簡單: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五年期間,他未曾申報所得稅,這在美國與其他大部分國家,都是重罪。確切來說,在美國,按慣例會被處以嚴重的罰緩與徒刑,而當威爾森第一次向律師坦承他的違法行為時,律師「馬上告訴我,在這一團混亂中,顯然最好的做法就是成為他國公民」。[43] 他未能遵守法律的理由軟弱無力,因為成年後的大部分歲月,他都是一個不受雇於人的自由作家。一九四三年底他在《紐約客》找到一份正職,那裡的收入會預扣稅款;一九四六年,他出版了小說《黑卡蒂郡回憶錄》(Memoirs of Hecate County),是他商業上的一大成功,在此之前,他的最高收入是在《新共和》裡做副主編的七千五百美元。然而,他就在這一年再婚了,得為兩次離婚支付費用,為此他花掉了《黑卡蒂郡回憶錄》得到的意外之財。他說當時這本書依然暢銷,打算等錢進來再來彌補他的繳稅義務,但這本書突然惹上了言語猥褻的麻煩,從此再無進項。因此他說:「我認為等我再多賺點錢,再來申報一九四五年以來的所得稅會比較好。」此事發生在一九五五年,當時《紐約客》出版了他對舊約抄本「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長期且備受讚揚的研究成果,匯編成一本成功的書。便是此時 他去見稅務律師,對其建議感到震撼:「當時我不知道我們的稅變得有多重,或是沒有申報所得的懲處有多嚴厲。」[44]
這是非常不尋常的招供。這人在整個一九三○年代針對社會、經濟與政治問題廣泛寫作,曾為當局熱烈地提供加重公共支出與主要產業國有化等建議,他還出版了一本大書《到芬蘭火車站去》,滿腔熱情地研究那些透過「奪走中產階級資產的革命」來改變一般人處境的理念,究竟是如何發展而來的。他怎麼看待他大力支持的「新政」(New Deal),國家如何在高支出下收支平衡?難道他感受不到對所有改革工作有其個人責任,尤其是那些像他這樣,直接表達對弱勢有道德義務的人?還有他贊同的馬克思主義者警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呢?還是他覺得這適用於他人,但不適用於自己。簡言之,這是一個偏愛人類群體,卻沒想過人類個體的情況嗎?如果是這樣,他也不必擔心,反正馬克思本人這輩子,似乎也沒付過一毛錢的所得稅。威爾森的態度事實上是知識分子中的一個引人矚目的例子,大多數知識分子在告訴世人這個世界該如何運行時,是以相當道德權威的語氣,認為這些建議的實際後果跟他們無關──這些建議是給「一般人」的。
用了兩個律師和一群會計,總計五年的時間,威爾森才結清國稅局的帳。國稅局自然沒讓他太好過,他們對他課了六萬九千美元的稅,補足了十年六%的利息,外加九○%的罰金──五○%罰詐欺行為,二五%是罰違法行為,五%是沒有申報,一○%是涉嫌低報所得。但這已經是相當輕微的處罰了,因為威爾森每一次沒有申報,都能判處一年徒刑。此外,他以貧窮和必須支付一萬六千美元的律師費為辯護理由,國稅局最後寬赦了他,以折衷方案只跟他清算了兩萬五千美元,所以他理當覺得自己很走運。但正好相反,他寫了一本謾罵的書,《冷戰與所得稅:異議》(The Cold War and the Income Tax: a Protest),這在各方面來說都是失去理智的回應。該書以最挑釁的方式,訴說徵稅的角色,讓他深刻了解現代國家的令人恐懼的殘酷與恐懼──但這是對一個富有想像力、且從事國家理論與實務研究的人來說,不該感到意外的。他以最沒說服力的道德立場來攻擊政府,卻在強力支持國家以人本主義者的立場進行擴張時,大幅地漠視其潛在的弊端,卻在自己因為疏失觸法時,起而抗議國家。這就是威爾森的態度,在他的書中,他為了替自己不一致的行為開脫,主張大部分的所得稅都被花在冷戰妄想症造成的國防支出了。但他後來也沒繳州所得稅,而這些稅金也沒有用在國防上面。他也忽略了這一點:他定居美國時,聯邦所得稅率急遽上升,是用來作為社會福利支出的。逃這種稅也具有道德正當性嗎?簡言之,這本書顯示威爾森最壞的一面,但可喜可賀,這位仁兄那時四十歲,基本上已經不再是個涉足政治的知識分子了。
也可以說,藉由回到他文人的真實角色,威爾森的熟年變得非常多產。包括一九五五年的《死海古卷》(The Scrolls of the Dead Sea)、一九五九年論印第安人聯盟的《向北美印第安人部族致歉》(Apologies to the Iroquois),以及一九六二年探討美國南北戰爭文學的《愛國的高爾》(Patriotic Gore)。這些書與其他著作都具有勇氣和勤勉的特性──研究死海古卷得學習希伯來語──還有對真理不偏離正道又持續不懈的追求。這件事本身就讓他有別於大部分知識分子了。更何況是威爾森的研究與寫作,集中在對人們強力、溫暖、敏銳與文明的關懷,而不是抽象的理念。正是這種關懷讓他的文學評論生動活潑,讀之有味。對威爾森來說,最好的情況是牢記這個領悟:書本不是脫離現實的存在,而是來自活生生的男男女女的所感所思,而理解他們的關鍵,取決於他們與作者的交互影響。理念的殘酷之處在於預設人類可以屈己以配合理念,卓越人文學科帶來的幫助,在於能從個人的啟發進一步發展為通則。威爾森以動人的才情文筆,探討埃德娜.米萊,提出了一個詩人該如何發揮作用的完美定義:
最重要的是深刻感受個人經歷,讓她得以對更普遍的人類經驗感同身受,挺身而出,成為人類心靈的發言人,大聲說出人類的困境與興衰。但作為一個人性表達方式的大師,透過語言本身的壯闊,她讓自己超然於普遍的困窘、壓迫與驚恐之外。[45]
是威爾森的人本主義,讓他得以理解這些過程,從而擺脫追尋太平盛事的謬論。
1 指蘇聯的五年計畫,蘇聯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九一年解體為止,共實行了十三個五年計畫。
2 猶太教禁止偶像崇拜。根據《出埃及記》,摩西為了領受十誡,離開以色列人四十晝夜。以色列人擔心他不再回來,造了金牛犢。摩西得知消息後,憤怒地摔碎寫有十誡的石板,並毀掉金牛犢。
3 莫斯科審判(Moscow trials)指三○年代蘇聯大清洗時期,由史達林主導的一系列「作秀公審」。
第十一章 戈蘭茲:苦於良知的出版大亨
Victor Gollancz 1893-1967
「我收俄羅斯的文稿,好壞都收,因為它們『正統』。我退了其他稿子,是有誠意的社會學家與正直的作家寫的,因為他們不是…… 身而為人,我很肯定這全是錯的。」 ── 戈蘭茲
逐一研究任何知識分子,會有種強烈感覺油然而生,就是他們欠缺對真實性的尊重。他們急於發揚救贖、超脫的真理,將真理的確立視為他們對人類的使命,他們對平凡、日常的實情(以客觀事實為代表)沒有太多耐心,這些實情妨礙了他們的說理論證。這些帶來不便、不重要的實情於是受到漠視、竄改,甚至蓄意隱匿。這當中最突出的例子,便是馬克思。但我們所檢視的知識分子,在某種程度上都因此受罪,唯一的例外是威爾森,但他或許根本不能算是知識分子。接下來兩位知識分子,其工作與生活都以欺騙(包括自欺)為核心,確切來說,欺騙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
第一位是維克多.戈蘭茲(Victor Gollancz),他之所以重要,不光是因為他自己孕育出一個突出的理念,也因為他是許多理念的代理人,這些理念成果明顯,讓人印象深刻,使社會意識到其重要性,他或許是我們這個世紀傑出的知識分子宣傳人員。他絕對不是邪惡的人,即便他做錯了,通常也會意識到錯誤,因而感到良心痛苦不安。但他的職涯顯示,欺騙在推廣千禧年式的太平盛世理念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多麼異乎尋常。即便在他有生之年,曾經與他往來的人,都知道他對真理可以多麼傲慢。但現在,多虧了他女兒莉維亞(Livia Gollancz)的誠實,公開了他的文章,也要感謝一流的傳記作家愛德華的巧妙處理與公正無私,我們才得以檢驗他欺騙的確切本質與程度。[1]
……
戈蘭茲的書確實都以各種欺騙讀者的「詭計」作為開頭。例如,盡量用「左翼」來代替「共產黨」。戈蘭茲的許多信裡也反映出徹底的箝制,而且經常伴隨著他自憐地反覆訴說他良心極度的痛苦,例如一封寫給戰地記者米勒(Webb Miller)的信,談到一本西班牙的書,他下令刪去他知道是實情的兩個章節。開頭說「要寫這封信,我很苦惱,幾乎是難為情」,他知道米勒的描寫「在任何方面都未誇大不實」,但「為了證明『共產黨人野蠻落後』的宣傳目的,這幾章許多段落極有可能被摘錄與大量引述」,「絕對很難避免」。他覺得他無法出版任何「對手陣營會趁機拿來宣傳」、任何會「削弱對共產黨人的支持」的東西。他補充說,米勒可能會認為這是在「玩弄真相,並不全然是如此:人必須考慮最終的結果」。最後他懇求「請原諒我」──就像他要露絲赦免他不該養著一個情婦。[19]
戈蘭茲有一些給作家與編輯的指令,儘管明顯是囑咐他們不要誠實,卻還是使人頭腦混亂──無疑是因為他的良心極度痛苦──完全看不出來是要叫他們對什麼事特別不誠實。例如對一個歷史參考書作者,他寫道:「我希望內容做到最大程度的公正,但我也希望我公正的作者保有激進的精神。」他補充說,「作家的激進主義」將給予他「保證,要是盡了一切努力,還是呈現某種政治傾向」,應該不會是「方向錯誤的傾向」。戈蘭茲實際上是在說,就像當時他的信中不斷暗示的,他希望他發行的書表面上沒有立場傾斜,而但實際上有。
這些在戈蘭茲的檔案中留存的信特別迷人,因為它們是少數得以一窺知識分子阻礙真相大白於世的直接證據,他知道自己這麼做是錯的,並訴諸理想高於真相,來為自己辯護。戈蘭茲很快就開始養成大規模不誠實的習慣,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上台後,他決定砍掉所有不賺錢或沒有宣傳目的的書目。他還展開大型冒險事業,主要是用來推銷社會主義和提升蘇聯的形象,首先是新蘇維埃叢書(New Soviet Library),這是由蘇聯大使館與政府直接安排的蘇聯作者,所寫的一系列大外宣叢書。但是在掌握內容上出現了預料之外的困難,因為該系列內容的構思期,適逢大清洗發生,許多被推舉的作者突然在古拉格群島(Gulag archipelago)失蹤,或是被行刑隊拘捕,有些稿子寄給戈蘭茲時作者名字是空白的,因為作家被處決了,等待正式替換後才填上。更膽戰心驚的挫折是蘇聯的檢控官(Andrei Vishinsky),他在史達林政權中所扮演的角色,猶如希特勒政權的人民法院院長弗萊斯勒(Roland Freisler),負責撰寫《蘇維埃的正義》(Soviet Justice)一冊,卻忙著批准前同志的死刑而沒空寫。當稿子終於寄達時,因為寫得太匆促拙劣而無法出版。戈蘭茲的讀者們很幸福,對這些問題渾然不知。
無論如何,這個書系推出時,戈蘭茲已經投入更大的冒險:成立左書俱樂部(Left Book Club),最初成立是為了反擊書商們不願意進貨極端左翼的宣傳書目。左書俱樂部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到三月間,發起漫天的廣告攻勢,與共產國際在歐洲實施的「人民陣線」策略一致:突然間,民主的社會主義黨派,例如工黨,不再是「社會的法西斯主義者」,反變成「鬥爭的同伴」了。加入左書俱樂部的會員接受為期至少半年、每月都購買半克朗由三位委員所選的書,這三人分別是戈蘭茲、斯特拉奇,與倫敦經濟學院的拉斯基(Harold Laski)教授,此外會員還能免費拿到每月的《左書新聞》(Left Book News),以及參加各種廣泛活動的權利──暑期學校、大集會、電影欣賞、討論小組、戲劇、合辦外國度假、午餐會以及俄語班,還可以使用俱樂部中心。[20] 一九三○年代是參與團體的美好時代。希特勒在德國之所以這麼成功,理由之一便是他為各種年齡與興趣,建立了許多團體,共產黨延續他的作法,而左書俱樂部恰恰顯示了這項技術多麼有效。戈蘭茲原本希望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之前吸收二千五百人訂購,實際上會員數是九千人,最後攀升至五萬七千人。俱樂部的影響甚至比這些數字更廣闊。在三○年代的媒體機構中,它是決定議題、指導趨勢的成功機構。然而,它的根基是一連串的謊言,第一個謊言是文宣資料上說,選書是「委員會一起選的,能充分代表大部分積極與嚴肅的『左派』運動意見」。事實上左書俱樂部進行一切措施的目的,都是為了共產黨的利益,斯特拉奇在那個時期完全受共產黨控制,[21] 而拉斯基是工黨成員,才剛入選工黨的全國執行委員會(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但後者在一九三一年改信馬克思主義,並且一路追隨共產黨路線,直到一九三九年。[22] 戈蘭茲在一九三八年之前,也一直都是個可靠的共黨同路人,他為共產黨機關報《工人日報》(DailyWorker)寫獻媚文章「我為什麼閱讀《工人日報》」,被拿來當作該報的宣傳資料。他標榜該報獻身於真相、正確度,以及對讀者智慧的信任(他知道上述全部無憑無據)並提到:「其特色是男人和女人,而非淑女與紳士。就我自身的部分,我遇過很多淑女與紳士,發現他們當中許多人都非常令人生厭,而該報品質特別煥然一新。」[23] 他也曾在一九三七年造訪俄羅斯,並斷言:「我第一次感到全然的幸福…… 因為這裡可以讓人忘卻世上其他地方的邪惡。」[24]
然而,戈蘭茲對左書俱樂部最大的實際貢獻,是用自己的人馬做俱樂部的職員。席拉.林德、埃米爾.伯恩斯(Emile Burns)、約翰.路易士(John Lewis)編輯了所有原稿,還有打理俱樂部所有團體的貝蒂.里德(Betty Reid),他們當時都是共產黨成員,或是受黨的控制。一切決策,就連芝麻蒜末的小事,都是跟共產黨高幹討論的。戈蘭茲經常直接受共產黨總書記波利特的指揮,這些大眾都不知道,左書俱樂部蓄意在提到共產黨員時說成是「社會主義者」,以隱藏他們跟共產黨的關連。入選的頭十五本書,除了三本不是,其餘都是共產黨員或祕密黨員所寫──這讓戈蘭茲憂慮,不是因為事實本身,而是擔心這會給人俱樂部並非獨立營運的印象。俱樂部公認的獨立性,確實是共產黨眼中最大的資產。杜特(R.Palme Dutt)是共產黨重要的思想家,曾在一封寫給斯特拉奇的信中,非常高興大眾相信俱樂部是「一家獨立的營利企業」,而非「特殊的政治大外宣機構」,這構成了對黨的價值。
第二個謊是戈蘭茲一再重申,整個左書俱樂部的組織,包括團體、集會與公開活動,「本質上是民主的」,這比迪比絲小姐和她的「辦公室蘇維埃」更有效。在這種標榜寡頭政治的表面下,實際上是戈蘭茲的一人專制,理由很簡單,因為他掌控財務。確切地說,他並沒有把左書俱樂部跟戈蘭茲股份有限公司的帳分開,俱樂部的進帳與經費全進了他的公司,結果便是無從得知戈蘭茲的事業到底是賠是賺。當有人批評戈蘭茲因此發了大財,他告他們誹謗。他在私人書信中告訴作者們他賠慘了,但又補充道:「以下是絕對的機密:從許多角度來看,比起讓大家知道我們正在賠錢,說我們現在獲利巨大比較不危險。」[25] 但他這麼做很可能只是為付給作者微薄、甚至沒付版稅,找個正當理由罷了。如果單就共同分擔管銷費用,以及幫忙促銷其他的書,我們必須假設左書俱樂部讓這家公司受惠。無論如何,戈蘭茲經手款項,並支付薪資與帳單,做一切事務的最終決定。俱樂部任何成員對任何事都有發言權的想法,這只是一個幻想。在找人編輯《左書新聞》時,他規定他必須「自動自發,加上絕對、馬上、毫無疑問地服從我的指令,不管這些指令對他來說有多愚蠢」。[26]
第三個謊言是約翰.斯特拉奇說的:「我們不希望僅僅因為不同意其結論,就拒選一本書。」扣除一、兩本工黨的書──如工黨領袖艾德禮受邀撰寫的《透視工黨》(The Labour Party in Perspective)──有壓倒性的證據顯示,恪守共產黨路線,通常是選書的主要標準。特別明目張膽的例子是德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塔爾海默(August Thalheimer)的《辯證唯物主義導論》(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al Materialism),戈蘭茲認為此書是正統的,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同意出版,但同時該作者在莫斯科捲入某些晦澀難明的爭端,波利特要戈蘭茲打壓這本書。這本書已經做了預告宣傳,戈蘭茲反對打壓,認為俱樂部的敵人會抓住沒有出版這個把柄,「證明左書俱樂部只是共產黨的分支」。波利特以他那假裝無產階級的口吻回答:「別出版!別在我得應付老畜生、大畜生跟主任牧師的血腥紅屁股的時候!」這裡指的是史達林、杜特,與備受崇敬的坎特伯里祭司長約翰遜(Hewlett Johnson)教士。結果戈蘭茲照辦了,壓下那本書,但後來寫了封發牢騷的信向波利特抱怨:「我痛很且不喜歡這麼做:我生來就是這樣,這種虛假不實會毀了我內在的一部分。」共產黨想要打壓的另一本書是《為什麼資本主義代表戰爭》(Why Capitalism Means War),是地位與資歷極高的社會主義者布萊爾斯福德(H.N.Brailsford)寫的,因為該書批評了莫斯科審判。一九三七年九月,當原稿拿給伯恩斯看時,就連他也建議大幅刪改這本書,但是黨仍然不接受。這回戈蘭茲也是全書封殺,他寫信給作者:「對這件事,我不能做出違心之舉。」出版一本批判莫斯科審判的書,就像「犯下違背聖靈的罪」。但是拉斯基本身對莫斯科審判不滿,作為布萊爾斯福德的老友,他說這本書一定要出版,並揚言要辭職,而這會毀了左書俱樂部「流行前線」書系的門面。所以戈蘭茲勉為其難地照拉斯基的要求做了,但是選在八月出版,而且完全不為此書宣傳,布萊爾斯福德說這是「在遺忘中埋葬了這本書」。戈蘭茲還發明了「技術性原因」一詞,是為了打壓倫納德.吳爾夫的一本書,因為書中有批判史達林的內容。但吳爾夫有自己就的出版社,而且比戈蘭茲更懂印刷,他拆穿了謊言,並揚言要是破壞協議,將會公開謊言訴諸輿論。戈蘭茲再次讓步,但還是設法讓這本書賣不起來。
事實上,左書俱樂部的出版品是以欺騙的方式,蓄意宣揚共產黨路線。就如同戈蘭茲寫給俱樂部教育書系,左派總部大學叢書(Left Home University Library)的編輯說的,「處理方式當然不該是做一個有攻擊性的馬克思主義者」。書的寫法應該是「讓讀者無論何時都將獲得正確的結論,讓還沒讀過的人,不會因為感覺『喔,又是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而遲疑」。戈蘭茲有時跟共產黨掌權者的關係極度緊密:有記錄顯示,他曾數度以現金匯款給波利特──「我在想今天早上你能否讓我拿到一些英鎊紙鈔。抱歉麻煩你了,戈蘭茲,但你是知道情況的。」[27] 共產黨的審查後來越審越細;例如後來的《工人報》(Worker)編輯坎貝爾(J.R.Campbell)便負責從圖書目錄中移除托洛斯基和其他「被排斥的人」的作品。戈蘭茲的行為,儘管被他的傳記作者稱為「大量可顯示有罪的資 料」無法辯解且有文件證明,但還是必須在脈絡裡理解。一九三○年代是謊言的時代,大大小小的謊言,比我們這個世紀的任何一個年代都還要多。納粹與蘇聯政府說謊的規模驚人,投入大量財務資源,雇用數以千計的知識分子,過去被讚揚獻身給真理的崇高機構,現在正在蓄意打壓真理。在倫敦,《泰晤士報》編輯道森(Geoffrey Dawson)的說法是,他自家通訊記者寫的東西,若可能破壞英德關係,就「不讓它上報」。在巴黎,知名的人權聯盟(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重要成員費利辛.查萊(Félicien Challaye),覺得自己必須辭職,以抗議該機構協助掩蓋史達林暴政的真相。[28] 共產黨人士經營專業的說謊組織,其具體目的是透過各種陣線組織,欺騙同情他們的知識分子,例如反帝大同盟(the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這種組織最初是柏林開始經營的,然後是希特勒主政後在巴黎出現,德國的共產主義者明岑伯格(Willi Muenzenberg),被《新政治家》編輯馬汀形容為「能力卓越的大外宣行家」,他的左右手捷克共產黨人卡茨(OttoKatz),被馬汀描述為「狂熱而殘忍的蘇聯政委」,並延攬了許多英國知識分子幫忙。[29] 這些人還包括前《泰晤士報》記者卡柯本(Claud Cockburn),他是左翼八卦雜誌《週刊報導》(TheWeek)的編輯,協助卡茨策畫全然虛構的新聞報導,例如摩洛哥的得土安(Tetouan)發生「反佛朗哥的暴動」。卡柯本後來將他的這些豐功偉業出版時,受到國會議員克羅斯曼(R.H.S.Crossman)的譴責,在《新聞紀事報》(News Chronicle)中說他不要臉,以編造謊言為樂。克羅斯曼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戰爭期間,正式加入了英國政府的「散布假訊息活動」(也就是說謊),他寫道:「骯髒的宣傳手法在戰爭中或許有其必要,但我們大部分人在實施時都很厭惡我們的作為。」克羅斯曼剛好是典型的知識分子,總是認為理念比人優先,缺乏對真相的強烈意見。卡柯本指責克羅斯曼的觀點是:「如果你能停止大笑,那就是宜人的道德立場。至少對我而言,看到一個人批評自己的大外宣謊言,這種奇景看起來頗幽默…… 但是能因為『厭惡自身行為』讓良心保持乾淨。」對卡柯本來說,為了理想奮鬥,那是值得為它去說謊的。[30](什麼理想!明岑伯格與卡茨雙雙被史達林以「叛國罪」賜死,卡茨被殺的理由是跟克勞德.卡柯本那種「西方帝國主義者」廝混。)
戈蘭茲不誠實的行為,必須在此背景下考察,這當中最臭名遠播的是他拒絕出版喬治.歐威爾的《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該書揭露共產主義者對付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的暴行。他不是唯一拒絕歐威爾的人,馬汀也拒絕刊登歐威爾探討相同議題的一系列文章,三十年後他依然捍衛他當時的決定:「在跟德國作戰期間,我寧願刊登戈培爾的文章,也不想刊登他的。」他還說服了他的文學編輯雷蒙.莫提默(Raymond Mortimer)拒登歐威爾所寫的「可疑」書評,但莫提默後來深感懊悔。[31] 戈蘭茲與歐威爾的關係持久,複雜、敵對又低劣而骯髒。早在左書俱樂部開始營運之前,他就出版了歐威爾的《通往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當他決定出版此書的俱樂部版本時,便決定要壓下書中異議的部分。雖然歐威爾不讓他這麼做,但他硬是出版了。他在俱樂部版本裡自己寫了篇導言,試圖以「中下階層的一員」的身分,解釋歐威爾書中的「錯誤」。先不管他是什麼階層(他肯定比歐威爾富裕很多),他此前此後都跟工人階層幾乎沒有接觸,因此這篇導讀特別不誠實。後來戈蘭茲深感羞愧,並在美國出版商轉載這篇導讀時勃然大怒。[32]
等到戈蘭茲跟歐威爾的爭吵來到最高峰時,他對於自己跟共產黨人的關係已經改變想法。會這樣有幾個理由。……
左書俱樂部在戈蘭茲與莫斯科決裂後,就不再是從前那個左書俱樂部了。人事已經分裂。席拉.林德、貝蒂.里德和約翰.路易士忠於共產黨,戈蘭茲決定不開除路易士與林德(此時已不再是他的情婦),但他還是很典型地好好利用這次機會降了他們的職等跟薪水,縮短他們的離職預告期。[34] 不像馬汀,直到死前都經常保護他三十幾歲的同路人,也不像克勞德.卡柯本嘲諷地誇耀自己的行為,戈蘭茲決定徹底悔改。一九四一年,他編了一本書,收錄了拉斯基、斯特拉奇和歐威爾的文章,名為《左派的反叛:對共產主義政策的考察與反駁》(The Betrayal of the Left: An Examination and Refutation of Communist Policy),在書中正式坦承左書俱樂部的罪行:
我收俄羅斯的文稿,好壞都收,因為它們「正統」。我退了其他稿子,是有誠意的社會學家與正直的作家寫的,因為他們不是…… 我只出版辯護莫斯科審判的書,並請批判這些書的社會主義者去別的地方出書…… 身而為人,我很肯定──當時我心裡很確定──這全是錯的。
戈蘭茲的改變心意與認罪有多真心與洗面革新,很難說。他肯定在戰爭期間經歷過靈魂的黑夜,並在前述的身體危機中達到最高潮。……
戈蘭茲戰後的職涯,實際上是垂死的沉淪。他寫了些相當賣座的書,但他自己的事業卻逐漸被擠下市場龍頭的位置。他沒跟上時代,看不出知識分子中崛起的新星。當路德維格.維根斯坦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寫信給他,指出他的公開論點中有缺失時,他信只回了一行「感謝來信,相信你是非常好意」,而且還拼錯這位哲學家的名字,以為他是個沒沒無聞的大學教員。[37] 他流失了一些最好的作家,錯過一些重要著作沒有簽下。他盛讚納博科夫(Nabokov)的《蘿莉塔》(Lolita)是「理解性靈的罕見傑作」,但沒買到版權便憤怒地斷定它是「一本極其齷齪下流的書,文學價值被過於高估」,最後還向《讀書人》(Bookman)雜誌譴責它是「色情文學」。他在一場廢除死刑的運動中扮演要角──這是他所有理想中投注心力最久的一個,也可能是他最重視關心的──但他在此一大膽冒險運動中的角色,卻被他討厭的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的光芒蓋過去,還有論述簡練確切又辯才無礙的加德納(Gerald Gardiner),這兩人獲得了所有的榮耀。更糟的是,一九五七年,核裁減運動剛成立時,戈蘭茲沒拿到高位,他當時離開了,要回去又覺得受辱,並發現自己甚至沒受邀加入委員會。他很重視這件事,說這是「令人震驚的羞辱」,讓他「心都碎了」。起初他怪罪老友約翰.柯林斯牧師,因為此人坐上了委員長的位置,而戈蘭茲認為這位子應該自己坐才對。但事實上柯林斯為了把他納入委員會而輸了一次爭取。然後戈蘭茲覺得該怪普利斯特里,把他們之間的不和追溯到一九三○年代初期普利斯特里的《英格蘭之旅》(English Journey)這本書,實際上普利斯特里只是核裁減運動眾多的發起人之一,而這群人都說,無論如何都不想與戈蘭茲共事。
到最後,幾乎所有人都發現戈蘭茲自我中心的虛榮令人無法忍受,尤其它的表現方式經常是令人不快的狂怒發飆。一九一九年時,他曾告訴姐夫,他無法決定是要做溫徹斯特公學的校長還是英國首相。[38] 實際上他很幸運,他的生意頭腦讓他得以建立一個不容任何人質疑他的私人獨裁體制,而他做不到讓其他人也喜歡他,其實一點也不重要。傳記作家愛德華引述了戈蘭茲檔案中一封典型的信,比任何對他性格描述都出色。他受邀且答應為紀念貝爾主教(Bishop Bell)發表演講,貝爾主教是唯一公開強力反對對德國進行區域轟炸的人,但由於出現了更有吸引力的邀約,戈蘭茲取消出席貝爾主教的紀念演說。理所當然,這惹惱了主辦人之一皮特曼(Pitman),他寫了封信斥責戈蘭茲。戈蘭茲回了封砲火猛烈的長信,指責皮特曼「在日落前含怒寫了這封信」,並以極其翔實的細節解釋,是如何駭人的負荷讓他取消了演講,他用最強烈的措辭,抗議皮特曼說他有「道德上的責任」去發表演說,還應該對這個任務產生熱情,他繼續說:「事實上,我正在發飆,因為我正在口述這封信。我必須說,這樣的評論顯然是不合理的。」接著又用了整整兩段指責皮特曼「非常傲慢無禮」,最後說:「我知道這封信開頭口氣還算客氣,但寫到最後卻過頭了。不管我勸過你什麼,我現在不想含怒到日落,所以指示我的祕書馬上寄出這封信。」這種自矜自負的長篇抨擊,在其他情況都相同的前提下,很可能是盧梭、馬克思或托爾斯泰的手筆。但這當中,有沒有一丁點自我嘲諷的可能呢?我們必須懷抱希望。
第十二章 海爾曼:隻手遮天的好萊塢女傑
Lillian Hellman 1905-1984
「她寫的每一個字都是謊話,包括『and』跟『that』。」 ── 麥卡錫,海爾曼的死對頭
戈蘭茲是為他的太平盛世目標竄改真相的知識分子,麗蓮.海爾曼(Lillian Hellman)的欺騙則似乎是來自天性。她和戈蘭茲一樣,參與了西方知識分子的一個陰謀:掩蓋恐怖的史達林主義。但和戈蘭茲不一樣的是,除了極其敷衍且虛偽的方式,她從未承認自己的錯誤與欺騙。的確,她所做的事,是更加明目張膽、厚顏無恥地說謊。或許有人會問:幹嘛為麗蓮.海爾曼費心呢?難道她不是虛構的藝術家嗎?也許對她來說杜撰有其必要,且現實世界與幻想可能重疊,一如海明威,另一個惡名昭彰的說謊家。對一個虛構作品的發明者,期待絕對的真實,是否公平呢?對海爾曼來說,可悲之處在於,在她的人生與工作中,漠視真相占據了核心位置。之所以很難忽略她,有兩個理由:第一,她是首位獲得國際地位的女性劇作家,並因此成為世界各地受過教育的女性象徵人物。第二,在她人生的最後數十年,她在美國知識分子圈子當中所達到的聲望與權力,後來很少人能企及,而部分原因,就出於她的欺騙。海爾曼引發了一個重大問題: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該對他們所欽佩的對象,期待與要求真相到什麼程度?
……
…… 海爾曼會不會像她的偶像史達林一樣,最終被體面而默默無聞的埋葬,還是她的謊言與一切,都將成為激進思想的奮鬥象徵?我們等著看吧。但是過去近兩百年的經驗顯示,這位老婦人身上,還有很多活力跟謊言呢。
第十三章 理性的潰逃
現代社會最重要的教訓之一,就是要小心知識分子。他們不是打破框架的個人主義者, 卻往往待在極端保守的同溫層。他們常常忘記一件事:「人」比他們的理念更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世俗知識分子的主要目標有重大改變,從烏托邦主義轉向享樂主義(hedonism),這種轉變剛開始很緩慢,然後逐步加速。要探其源頭,最好研究三位英國作家的觀點與他們的關係,他們剛好都出生於一九○三年:喬治・歐威爾,伊夫林・沃與西里爾・康諾利,他們可能會分別被描述為舊知識分子、反智論者與新知識分子。沃是在歐威爾已經罹患致命疾病後才開始跟他謹慎地交往,但他跟康諾利整個成年生涯都爭吵不休,而歐威爾跟康諾利在學生時期就彼此認識。這三位作家彼此都始終抱持著猜忌、懷疑與偶爾羨嫉的眼光。康諾利覺得自己是這三人中的失敗者,他在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書題上一個自憐的對句,寄給戲劇評論家沃斯理(T.C.Worsley):
在伊頓有歐威爾,在牛津有沃此前與之後,他都無足輕重 [1]
但這完全不是事實。在某些方面,事後證明,他在三人當中最舉足輕重。
……
然而,隨之而來的是史達林一聲令下,共產黨便要清洗無政府主義者的駭人經歷,歐威爾的數千名同志不是被謀殺,就是下獄遭受虐待與處決。他自己幸運逃過一死。而對他同樣有啟發的是,他返回英格蘭後,發現要把他對這些悲慘事件的記敘出版,很困難。無論是左書俱樂部的戈蘭茲,還是《新政治家》的馬汀──在大不列顛不斷傳播進步主張的兩大機構──都不容他說出真相,他不得不去找其他地方。歐威爾總是把經驗擺在理論之前,而這事件證實了他一直以來都是對的。理論告誡左派,行使權力時要行為正派、尊重事實。而經驗卻向他證明,左派有能力做到某種程度的不公義,和一種迄今幾乎無人知曉的殘酷,只有德國納粹極端錯誤的罪行能夠相提並論,而且他們還會為了維護更高的真理,迫切地打壓真相。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的事已經證實,經驗讓所有價值觀與忠誠的行為都變得令人困惑,也讓他在此事件中學會,人比抽象的理念更重要。這是他打從骨子裡一直都有的感受。歐威爾從未完全背棄過他的信念,即認為藉由強力推動理念,可以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從這個角度來說,他依然是一個知識分子。但他所抨擊的主軸,已經從既存的、傳統的、資本主義者的社會,轉向列寧之流的知識分子設法借屍還魂的、那種騙人的烏托邦。他的兩部傑作,《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本質上是批判現實化的抽象概念,批判烏托邦裡的極權主義對思想與人身的控制,以及(照他的說法)對於「應該服從中央集權的經濟」之誤解。[10]
這樣的重心轉移,就其本身而論,必然使歐威爾高度地批判知識分子。這很符合他的性格,他的性格更接近於有團隊精神的軍人,而非放蕩不羈的浪子。他的作品常常可見離題,比如關於龐德他說:「就算是詩人,也有權要求過正常的舒適生活。」確實,他的格言之一,是窮人和「普通百姓」往往比起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對他所謂的「常見禮儀」有更強烈的感受,也更重視一般的美德,例如誠信、忠心與真實。當他在一九五○年過世時,大家並不清楚他的終極政治目標,他也依然被模糊地歸類為一個左翼知識分子。隨著他聲譽日隆,左派與右派爭執起來(實際上到現在都還在爭),他到底效忠於哪一方。但是從他死後四十年以來,他逐漸被拿來當作責備左派知識分子思想的事實依據。那些對自己這一類人有團結精神的知識分子們,長期以來一直都把他視為敵人,例如瑪麗.麥卡錫,讀她談歐威爾的文章,有時會對她政治理念中強烈的階級意識,感到非常困惑,她說歐威爾「性格保守,舉止、穿著與思想完全不像一個退休的陸軍上校或工人那樣極端」,他是「打從一開始就對藝術一竅不通的人。他確實對藝術一竅不通」,而他的社會主義是「一個未經檢驗的理念,是假充內行去思考自己不熟悉的題目,純粹是在發牢騷」。他追打史達林主義者,是偶然間「單憑個人好惡的產物」,他的「政治失敗…… 是思想的失敗」。要是他還活著「一定會走向右派」,所以「對他來說死去或許是好事」。[11](最後一個想法──死比反赤化好,是典型知識分子對於事情的輕重緩急如何取捨的顯著例子。)
專業的知識分子們與歐威爾漸行漸遠,有一個理由是歐威爾越來越篤定,繼續尋找政治處方固然沒錯,「就像醫師必須努力拯救一個將死之人」,但也得開始「意識到政治行為多半是非理性的」,因此知識分子在強制執行他們習以為常的解決方案時,通常成效並不大。[12] 但是當知識分子對歐威爾越來越感到疑心,反對派──那些文學家,如果你喜歡這個稱呼──反倒開始對他感興趣。例如伊夫林.沃,就從未低估非理性在人生當中的重要性。他開始跟歐威爾通信,去醫院探視他。要是歐威爾還活著,他們的友誼應該會越加深厚。他們頭一次合作,是因為他們都很欣賞作家伍德豪斯(P.G.Wodehouse),也都覺得他不該因為愚蠢的戰時廣播(跟艾茲拉.龐德相比,他相當無害)而被迫害。在這個案子裡,兩人都主張獨立的個人,必須優先於「意識形態的是非」這種抽象概念。沃很快就看出歐威爾會成為知識分子階層的潛在叛逃者,他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一日的日記中提到:「我跟我那共產主義者的堂兄卡柯本吃飯,他警告我別碰托洛斯基主義的文學,於是我讀了歐威爾的《動物農莊》,而且非常喜歡。」[13] 他也看出《一九八四》的威力,儘管他無法相信在歐威爾所描繪的暴政裡,宗教精神無法在參與抵抗中倖存下來。他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七日寫給歐威爾的信中提出論點,補充說:「瞧你的書讓我多激動,激動到冒險長篇大論地佈道。」[14]
歐威爾拖了很久才不甘願地接受:烏托邦主義的失敗,是因為人類行為在根本上是不理性的──這是沃成年後大部分人生一直大聲疾呼的論點。確實,從沒有卓越的作家,甚至包括吉卜林,對反智的立場提出過這麼清楚的說明。沃和歐威爾一樣,相信個人經驗,相信眼見為憑,反對理論上的憑空想像。值得一提的是,儘管他沒有像歐威爾一樣,刻意跟受壓迫者一起生活,但他是一個重度旅遊者,經常造訪偏遠困苦的地區;他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從書本讀來的,跟自己實際見聞的一樣多。在書寫嚴肅的議題時,他對真相也有非比尋常的尊重。他一九三九發表了一部明確的政治作品,探討墨西哥的革命政權,書名叫《合法搶劫》(Robbery Under Law),在全書之前加上給讀者的警語,坦言他寫這個主題的背景為何,以及這資歷讓他看起來多麼不夠格,他請讀者留意那些觀點與他不同的著作,並警告他們不要單看他的說法,就為墨西哥目前的情況下判斷。他強調他強烈反對「堅定的」文學,他說,許多讀者「對享有新聞自由已經厭倦」,決定藉由成立讀書俱樂部來「自願受審查」(他心裡想的是戈蘭茲的左書俱樂部)好讓他們「無論讀了什麼,都有絕對的信心,能更加鞏固既存的定見」。因此,為了對他的讀者公平起見,沃認為,先概述自己的信念是恰當的。 他說他是保守主義者,他在墨西哥的所見所聞都強化了他這個信念:人類天生就是「流亡者,在這個地球上絕對不會自給自足或完滿」。他認為人類幸福的契機「不受其生活的政治與經濟情況影響」,而且人的狀態要是突然改變,多半會變得更糟,還常常「是錯的人,為了錯的理由倡議改變」。他相信政府:「人們要一起生活,不能沒有規則」,但是這些規則「應該僅維持在安全的最低限度」,「沒有一種宣稱由神所建立政府」會「比其他政府更好」。另外,「社會中的無政府主義成分」非常強大,「所以必須時時刻刻維護和平」。財富與地位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探討消弭這種不平等的好處沒有意義」。事實上,人會「自然地為自己安排所屬的階層」,這是「一切合作共事的必要」。戰爭與掠奪一樣不可避免。藝術也是人類天生就有的功能,而且「多麼湊巧」,最偉大的藝術都是在「政治殘暴專橫的制度下」產生的,儘管「我不認為這跟任何特定制度有所關連」。最後,沃說他是個愛國者,他不認為大不列顛的繁榮昌盛必然會不利於其他人,要是偶爾有,那麼「我希望繁榮的是大不列顛,而不是她的對手」。
沃便這樣說明了社會過去的樣貌和它必然會如何,以及他對此的回應。他確實有他個人的、理想化的願景,但身為一個反智論者,他也坦言這是不可能實現的。他的理想社會,一如他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一本書前言所說的,有四個階層。首位是「榮譽與正義的泉源」,緊接在後的是「由符合前述要求的男女擔任公職,他們是傳統、道德規範與美德的守衛」。他們必須「為犧牲做準備」,但受到保護,不受「世襲傳承之腐敗與野心的影響」。他們是「藝術的養育者,民風的審查者」。在他們之下是「工業與學術階級」,自幼便受訓「養成誠實的習慣」。最底層是手工勞動者,「對自身技藝自豪,也因為一起效忠最高統治者,對位階在他們之上的人感到驕傲」。沃藉由主張這樣的理想社會斷定,這個社會將永久存在:「一般而言,一個男人最適合做的事,是他看過父親執行過的任務。」但是這樣的理想「歷史中不曾有過,將來也不會有」,而且「我們每一年都越來越偏離這個理想」。他並非失敗主義者,他說他不想只是哀嘆,而屈服於時代的精神:「因為時代精神是由該時代的人所構成的,而越是強力表達對流行風氣的異議,就越有可能使它從有害的路徑轉向。」[15]
……
如今,這類知識分子有一個特色,就是當他們跨出自身專業時,卻看不到怪異與不妥之處:他們在自身專業中是公認的大師,但對公共事務的意見,他們的話語權不該比任何人都大。他們確實老是聲稱,他們的專業知識給了他們寶貴的洞察力,像羅素肯定認為他的哲學技能,讓他覺得他對人類諸多事務的忠告值得聽從──一九七一年杭士基在他的羅素講座(RussellLectures)就是這麼背書的。[76] 沙特則認為存在主義與冷戰所引發的道德問題,以及我們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回應,有直接的關連性。杭士基接著得出結論,他研究語言通用性的作品本身,就是美國對越南政策不道德的重要證據。怎麼會?嗯,好吧,杭士基主張,這取決於你接受哪一種知識理論,如果心智在出生時確實是一張白紙,則人類也可說是一片黏土,能隨我們高興捏塑,那麼人類就是政府當局、公司經理與中央委員會的技術官僚眼中,適合進行杭士基所謂的「行為塑造」的對象。[77] 另一方面,如果男女擁有的天生心智構造是一樣的,對文化與社會的模式有本能的需求,則這種國家的努力終將失敗,但在失敗的過程中,我們的發展將會受阻礙,並帶來可怕的殘酷行為。美國企圖將自己的意志與特殊的社會、文化與政治發展模式,強加於中南半島的人民身上。
任何研究知識分子職涯的人,都會在其中鬱悶地發現許多似曾相識之處:需要多罕見的執拗與剛愎,才能得出杭士基的結論。他主張的內在構造要是成立,那簡直是把反對任何類型的社會工程視為通例。也的確,因為諸多理由,社會工程已經成為現代史上顯著的騙局與最大的詛咒了。在二十世紀,社會工程在蘇維埃俄國、納粹德國與共產中國等地,殺死了幾千萬無辜人民,但「反社會工程」是西方民主國家(這全都得怪他們)最不願意擁護的觀念。恰恰相反,社會工程是烏托邦知識分子的發明,他們認為可以自然而然地,光憑一己的理性重新塑造這個世界。而這是極權主義傳統與生俱來的權利,由盧梭開拓、馬克思將之系統化,列寧將之制度化,列寧的繼任者們實施社會工程超過七十年,他們沒有取得成功,確實更加證明了杭士基的通則。社會工程,或是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執政的中國製造了上百萬具屍體,也同樣失敗了,雖然採行社會工程的,是沒有言論自由的極權政府,但剛開始時,整體計畫是知識分子做出來的。例如種族隔離政策,是由南非斯泰倫博斯大學(Stellenbosch University)社會心理系發展出的精細、現代的做法,在非洲其他地方──坦尚尼亞的烏賈馬運動(Ujaama)、迦納的自覺主義(Consciencism)、塞內加爾的黑人運動(Négritude)與尚比亞的人道主義等等──當地大學的政治或社會學系,也都規畫出類似的制度。美國插手中南半島事務,儘管一直都很輕率,實施起來也肯定很愚蠢,但其出發點,正是為了拯救當地人民免遭社會工程荼毒。
杭士基對於這樣的論證視而不見,他並不關心極權主義者企圖壓迫或改變人類與生俱來的特質。他主張,自由主義的民主、放任主義的國家,跟極權專制一樣會引起反對,因為資本主義制度做為構成整體的必要環節,其所提供的要素跟高壓政治一樣,會製造一些情況,剝奪或拒絕給予人民自我實現的權利。越戰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壓迫一小群試圖回應本能欲望的人民。這當然注定會失敗,同時又會讓人民遭受無法形容的殘酷。[78]
美國想要確保中南半島有機會發展民主社會,但像杭士基這樣的知識分子所提出的論據,肯定會大大重挫美國原本的強烈決心。一如那些支持美國介入的人一直以來所預料的,美軍一徹退,社會工程師們馬上進駐。甚至,美軍的撤退在柬埔寨造成的直接結果,是在一九七五年發生的重大罪行,堪稱百年一見的奇觀:一群在沙特的巴黎受過教育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現在執掌一支令人畏懼的軍隊,以史達林或毛澤東的殘酷標準,進行了一場社會工程的實驗。
杭士基對此暴行的回應很有啟發,既複雜又扭曲,以大量令人困惑的筆墨噴射而成。事實上,這與馬克思、恩格斯及其追隨者,聽聞「馬克思的演講蓄意竄改格萊斯頓財政預算」後的反應驚人的相似。要解釋詳情會太占篇幅,但重點相當簡單,按照杭士基的定義,美國已經達到了形上學的地位,成為中南半島的反派角色。因此,除非找到方法證明美國對柬埔寨的大屠殺有直接或間接的責任,否則就不該承認柬埔寨發生過大屠殺。
杭士基跟他的夥伴之回應,是經歷這四個階段推展而來的。[79] 一、沒有大屠殺,這是西方為了大外宣捏造的。二、是有小規模的殺戮,但是「柬埔寨的苦難已經被憤世嫉俗的西方人道主義者所利用,他們迫切希望克服『越南症候群』」。三、殺戮的規模比最初想的還要龐大,而且這是美國戰爭罪行對農民殘酷對待的結果。四、杭士基最後被迫引述「少數可信的柬埔寨學者之一」,透過巧妙的變更年表,「證實」了最慘烈的大屠殺不是發生在一九七五年,而是「一九七八年中」,而且發生大屠殺不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傳統主義者、種族主義者與反越戰之故」。該政權在當時已經「喪失曾有的一切馬克思主義色彩」,並淪為「極度盲目愛國的貧農民粹主義的工具」。就其本身而論,它「最終」獲得了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認可,中情局為了大外宣,從對大屠殺言過其實,轉變成積極從事殺戮的犯罪。總之,波爾布特的罪實際上是美國的罪,證明完畢。
到一九八○年代中期時,杭士基對越南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到尼加拉瓜上,但他讓自己超出了等著與他嚴肅辯論的人的理解範圍,也因此不上了羅素與沙特的可悲路線。所以,又一個曾經傲視群倫的知識分子,埋首開拓著極端主義的荒漠,有點像是年邁的托爾斯泰,在亞斯納亞─博利亞納莊園發出怒火與難以理解的話語。許多夢想太平盛世的知識分子的人生,似乎都有過一段凶險的更年期,一種大腦的活動終止期,或許可稱之為理性的潰逃。
***
我們現在來到了調查的終點。距今大約兩百年前,世俗知識分子開始取代舊有的知識階層,成為人類的嚮導與良師。我們已經看了許多企圖給予人類忠告的個案,檢視了他們擔當此一任務道德與判斷力的資格。尤其,我們考察了他們對真相的態度,他們尋找與評判證據的方式,他們對全體人類、特別是對個別的人的反應,他們對待朋友、同事、僕人,以及最重要的──對待自己家人的方式。我們也已經碰觸到遵循他們建議所帶來的社會與政治後果。
該推斷出什麼結論?讀者將自行評判。但我認為,現在有一種公眾的懷疑態度,當知識分子站出來向我們鼓吹時,在一般民眾當中,有一股越來越大的趨勢,是會去質疑學者、作家與哲學家的正當性,就算他們可能學識地位相當出眾,我們卻對於他們告訴我們該如何表現得體、如何處理我們的事務感到懷疑。有一種信念似乎正在普及:認為知識分子作為導師卻未必更有智慧,作為榜樣也沒有比醫師或過去的神職人員更值得尊敬。我也抱持這種遲疑態度,在街上隨機挑十幾個人,問他們對於道德與政治議題的看法,可能就會看見一種知識分子圈的橫剖面,至少他們看法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但我會提出更極端的意見。我們這個悲慘的世紀,最重要的教訓之一就是要當心知識分子,他們為了謀求人類的進步,犧牲了數百萬無辜性命。他們不但應該遠離權力的槓桿,在他們試圖提供集體建議時,也該成為特別受質疑的對象。當心知識分子組成的委員會、大會與同盟,別相信他們連成一氣所發表的公開聲明,不要太相信他們對政治領袖與重要事件的判斷。知識分子絕不是高度個人主義與不墨守成規的人,他們遵循某種常規的行為模式。整體而言,他們往往待在極端墨守成規的人所組成的圈子,而圈子是由那些認同他們的企圖與價值觀的人組成的。這就是導致他們「全體」這麼危險的原因,因為「全體」能讓他們營造輿論的風向與形成占優勢的正統說法,這些說法本身經常產生不理性又具破壞力的行動方針。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一直記得,知識分子習慣遺忘一件事:「人」比理念重要,而且必須優先考量。所有專制體制中最糟糕的,就是為了無情殘暴的思想專制。